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杂识
杂识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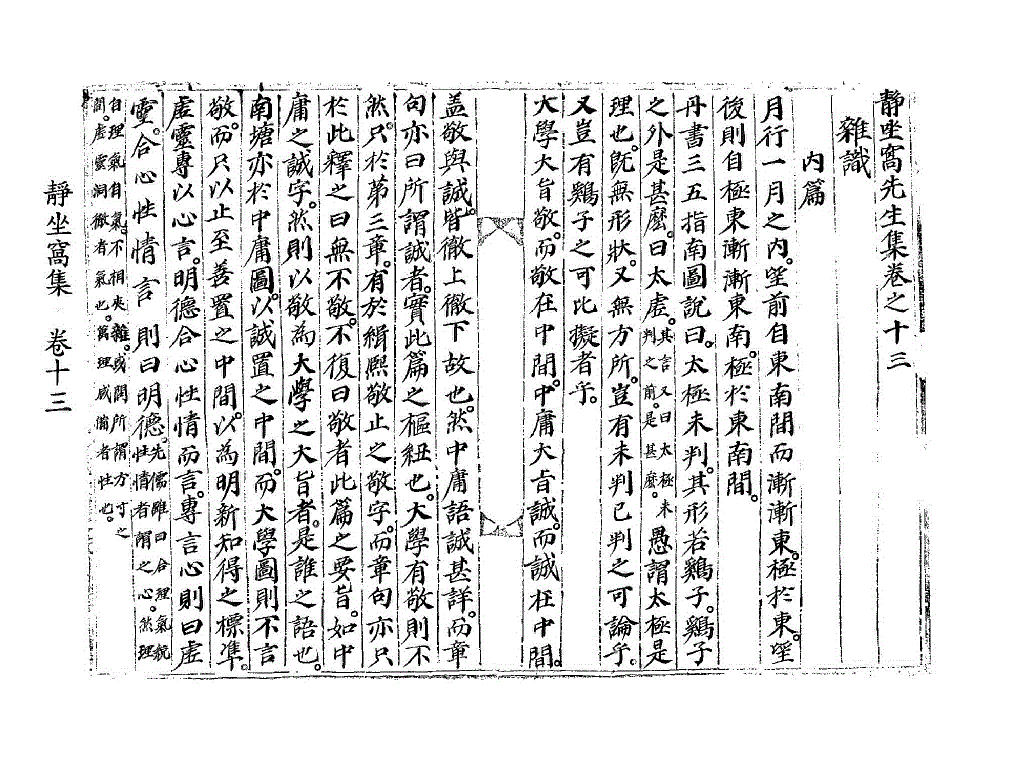 内篇
内篇月行一月之内。望前自东南间而渐渐东。极于东。望后则自极东渐渐东南。极于东南间。
丹书三五指南图说曰。太极未判。其形若鸡子。鸡子之外是甚么。曰太虚。(其言又曰太极未判之前。是甚么。)愚谓太极是理也。既无形状。又无方所。岂有未判已判之可论乎。又岂有鸡子之可比拟者乎。
大学大旨敬。而敬在中间。中庸大旨诚。而诚在中间。盖敬与诚。皆彻上彻下故也。然中庸语诚甚详。而章句亦曰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大学有敬则不然。只于第三章。有于缉熙敬止之敬字。而章句亦只于此释之曰无不敬。不复曰敬者此篇之要旨。如中庸之诚字。然则以敬为大学之大旨者。是谁之语也。
南塘亦于中庸图。以诚置之中间。而大学图则不言敬。而只以止至善置之中间。以为明新知得之标准。
虚灵专以心言。明德合心性情而言。专言心则曰虚灵。合心性情言则曰明德。(先儒虽曰合理气统性情者谓之心。然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或问所谓方寸之间。虚灵洞彻者气也。万理咸备者性也。)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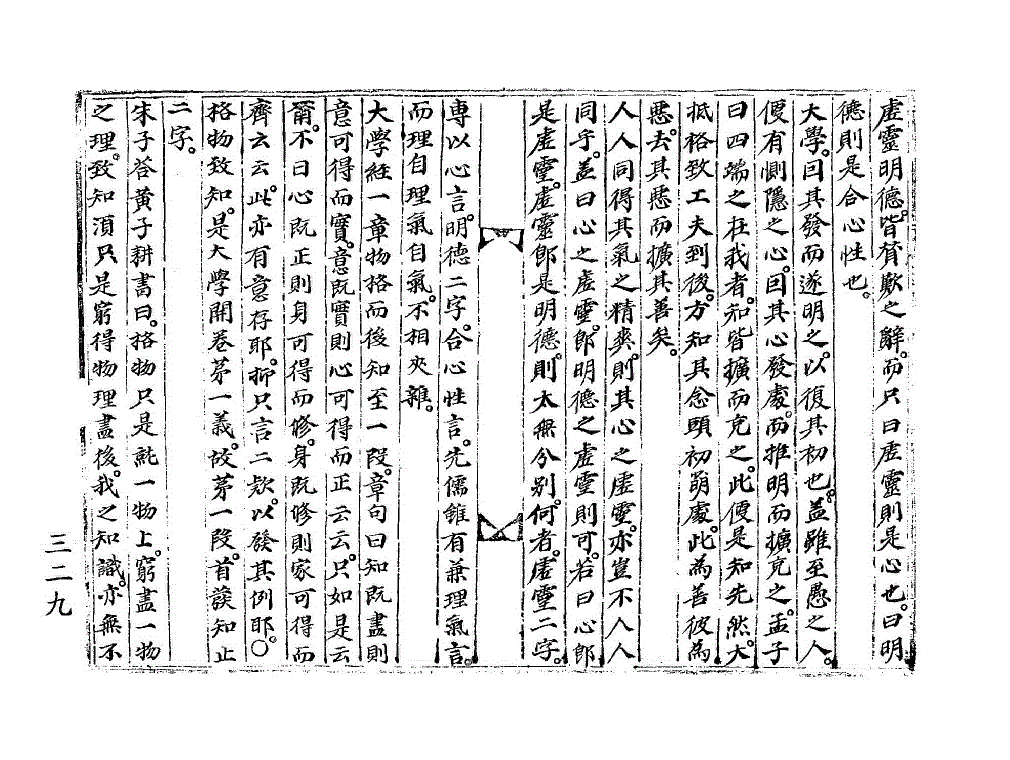 虚灵明德。皆赞叹之辞。而只曰虚灵则是心也。曰明德则是合心性也。
虚灵明德。皆赞叹之辞。而只曰虚灵则是心也。曰明德则是合心性也。大学。因其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盖虽至愚之人。便有恻隐之心。因其心发处。而推明而扩充之。孟子曰四端之在我者。知皆扩而充之。此便是知先然。大抵格致工夫到后。方知其念头初萌处。此为善彼为恶。去其恶而扩其善矣。
人人同得其气之精爽。则其心之虚灵。亦岂不人人同乎。盖曰心之虚灵。即明德之虚灵则可。若曰心即是虚灵。虚灵即是明德。则太无分别。何者。虚灵二字。专以心言。明德二字。合心性言。先儒虽有兼理气言。而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
大学经一章物格而后知至一段。章句曰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云云。只如是云尔。不曰心既正则身可得而修。身既修则家可得而齐云云。此亦有意存耶。抑只言二款。以发其例耶。○格物致知。是大学开卷第一义。故第一段。首发知止二字。
朱子答黄子耕书曰。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须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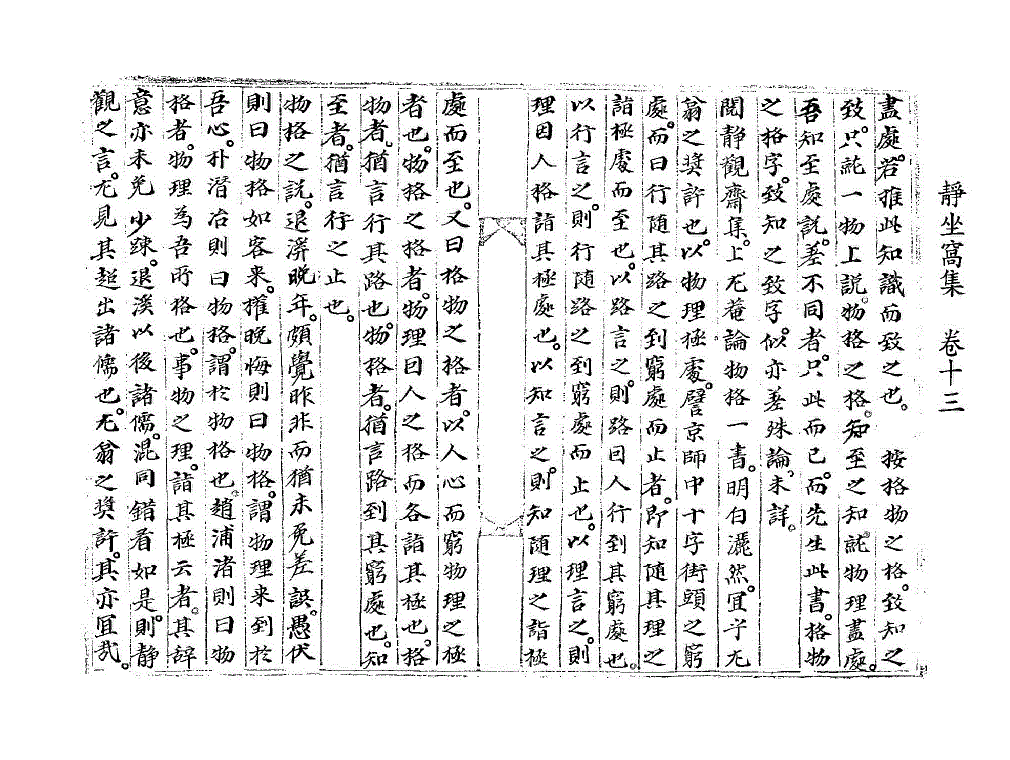 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 按格物之格。致知之致。只就一物上说。物格之格。知至之知。就物理尽处。吾知至处说。差不同者。只此而已。而先生此书。格物之格字。致知之致字。似亦差殊论。未详。
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 按格物之格。致知之致。只就一物上说。物格之格。知至之知。就物理尽处。吾知至处说。差不同者。只此而已。而先生此书。格物之格字。致知之致字。似亦差殊论。未详。阅静观斋集。上尤庵论物格一书。明白洒然。宜乎尤翁之奖许也。以物理极处。譬京师中十字街头之穷处。而曰行随其路之到穷处而止者。即知随其理之诣极处而至也。以路言之。则路因人行到其穷处也。以行言之。则行随路之到穷处而止也。以理言之。则理因人格诣其极处也。以知言之。则知随理之诣极处而至也。又曰格物之格者。以人心而穷物理之极者也。物格之格者。物理因人之格而各诣其极也。格物者。犹言行其路也。物格者。犹言路到其穷处也。知至者。犹言行之止也。
物格之说。退溪晚年。颇觉昨非而犹未免差误。愚伏则曰物格如客来。权晚悔则曰物格。谓物理来到于吾心。朴潜冶则曰物格。谓于物格也。赵浦渚则曰物格者。物理为吾所格也。事物之理。诣其极云者。其辞意亦未免少疏。退溪以后诸儒。混同错看如是。则静观之言。尤见其超出诸儒也。尤翁之奖许。其亦宜哉。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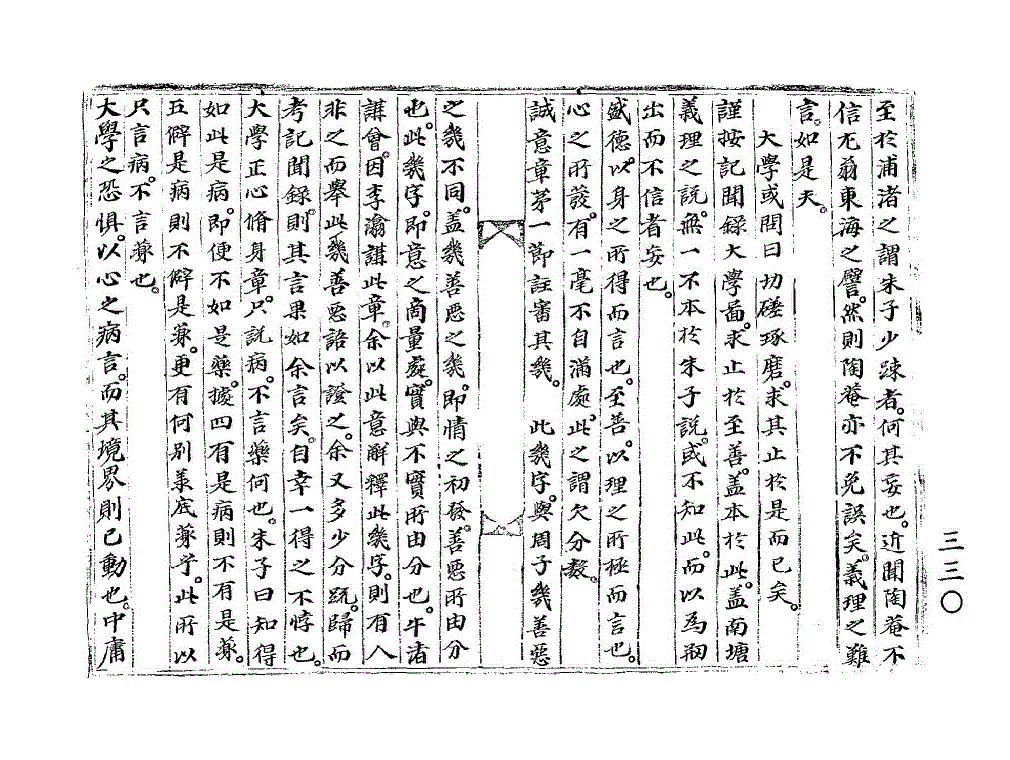 至于浦渚之谓朱子少疏者。何其妄也。近闻陶庵不信尤翁东海之譬。然则陶庵亦不免误矣。义理之难言。如是夫。
至于浦渚之谓朱子少疏者。何其妄也。近闻陶庵不信尤翁东海之譬。然则陶庵亦不免误矣。义理之难言。如是夫。大学或问曰切磋琢磨。求其止于是而已矣。
谨按记闻录大学啚。求止于至善。盖本于此。盖南塘义理之说。无一不本于朱子说。或不知此。而以为刱出而不信者妄也。
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极而言也。
心之所发。有一毫不自满处。此之谓欠分数。
诚意章第一节注审其几。 此几字。与周子几善恶之几不同。盖几善恶之几。即情之初发。善恶所由分也。此几字。即意之商量处。实与不实所由分也。牛渚讲会。因李潝讲此章。余以此意解释此几字。则有人非之而举此几善恶语以證之。余又多少分疏。归而考记闻录。则其言果如余言矣。自幸一得之不悖也。
大学正心脩身章。只说病。不言药何也。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是药。据四有是病则不有是药。五僻是病则不僻是药。更有何别羕底药乎。此所以只言病。不言药也。
大学之恐惧。以心之病言。而其境界则已动也。中庸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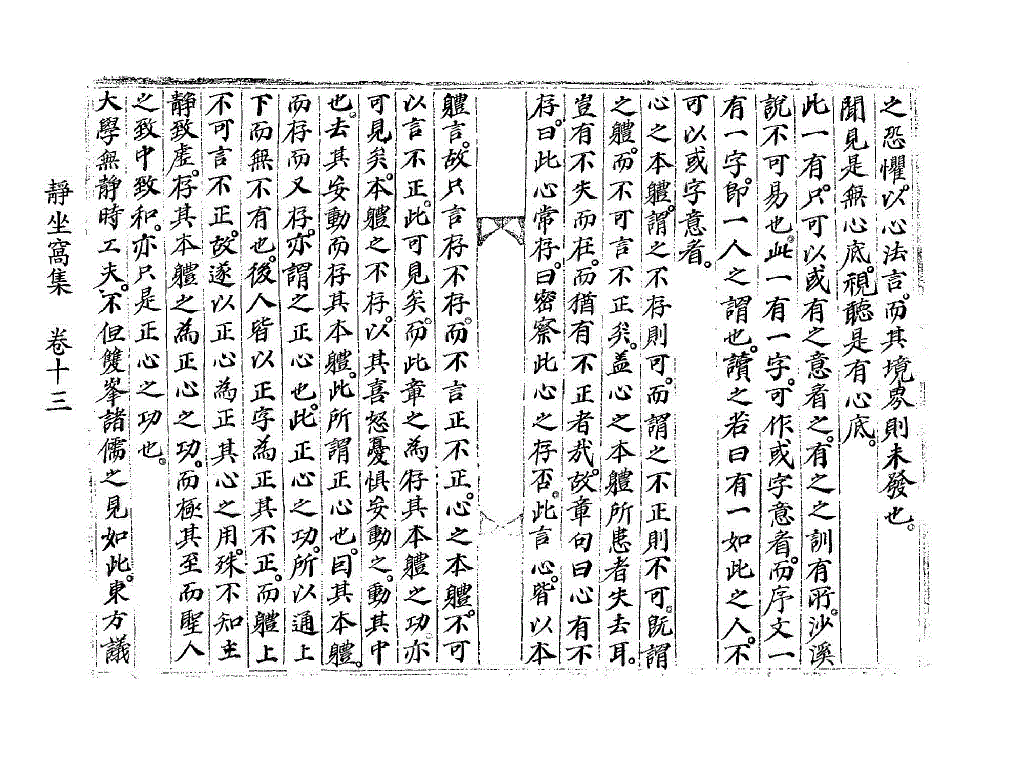 之恐惧。以心法言。而其境界则未发也。
之恐惧。以心法言。而其境界则未发也。闻见是无心底。视听是有心底。
此一有。只可以或有之意看之。有之之训有所。沙溪说不可易也。此一有一字。可作或字意看。而序文一有一字。即一人之谓也。读之若曰有一如此之人。不可以或字意看。
心之本体。谓之不存则可。而谓之不正则不可。既谓之体。而不可言不正矣。盖心之本体所患者失去耳。岂有不失而在。而犹有不正者哉。故章句曰心有不存。曰此心常存。曰密察此心之存否。此言心。皆以本体言。故只言存不存。而不言正不正。心之本体。不可以言不正。此可见矣。而此章之为存其本体之功。亦可见矣。本体之不存。以其喜怒忧惧妄动之。动其中也。去其妄动而存其本体。此所谓正心也。因其本体。而存而又存。亦谓之正心也。此正心之功。所以通上下而无不有也。后人皆以正字为正其不正。而体上不可言不正。故遂以正心为正其心之用。殊不知主静致虚。存其本体之为正心之功。而极其至而圣人之致中致和。亦只是正心之功也。
大学无静时工夫。不但双峰诸儒之见如此。东方议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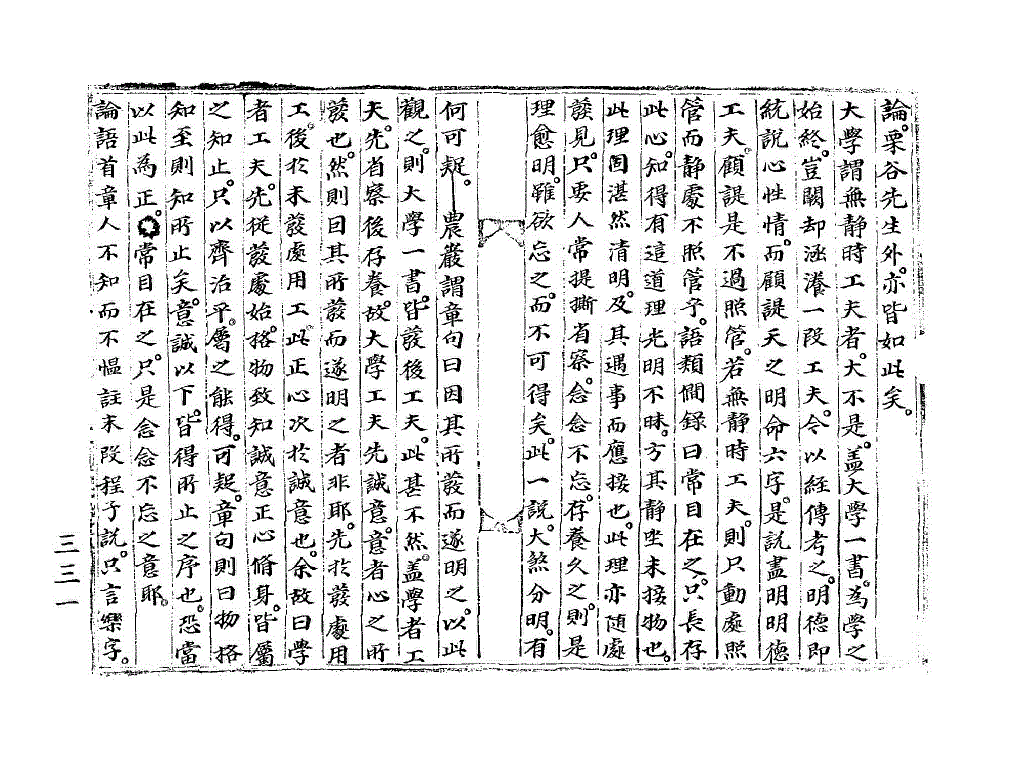 论。栗谷先生外。亦皆如此矣。
论。栗谷先生外。亦皆如此矣。大学谓无静时工夫者。大不是。盖大学一书。为学之始终。岂阙却涵瀁一段工夫。今以经传考之。明德即统说心性情。而顾諟天之明命六字。是说尽明明德工夫。顾諟是不过照管。若无静时工夫。则只动处照管而静处不照管乎。语类僩录曰常目在之。只长存此心。知得有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静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应接也。此理亦随处发见。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养久之。则是理愈明。虽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此一说。大煞分明。有何可疑。农岩谓章句曰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此观之。则大学一书。皆发后工夫。此甚不然。盖学者工夫。先省察后存养。故大学工夫先诚意。意者心之所发也。然则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者非耶。先于发处用工。后于未发处用工。此正心次于诚意也。余故曰学者工夫。先从发处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脩身。皆属之知止。只以齐治平。属之能得。可疑。章句则曰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恐当以此为正。○常目在之。只是念念不忘之意耶。
论语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注末段程子说。只言乐字。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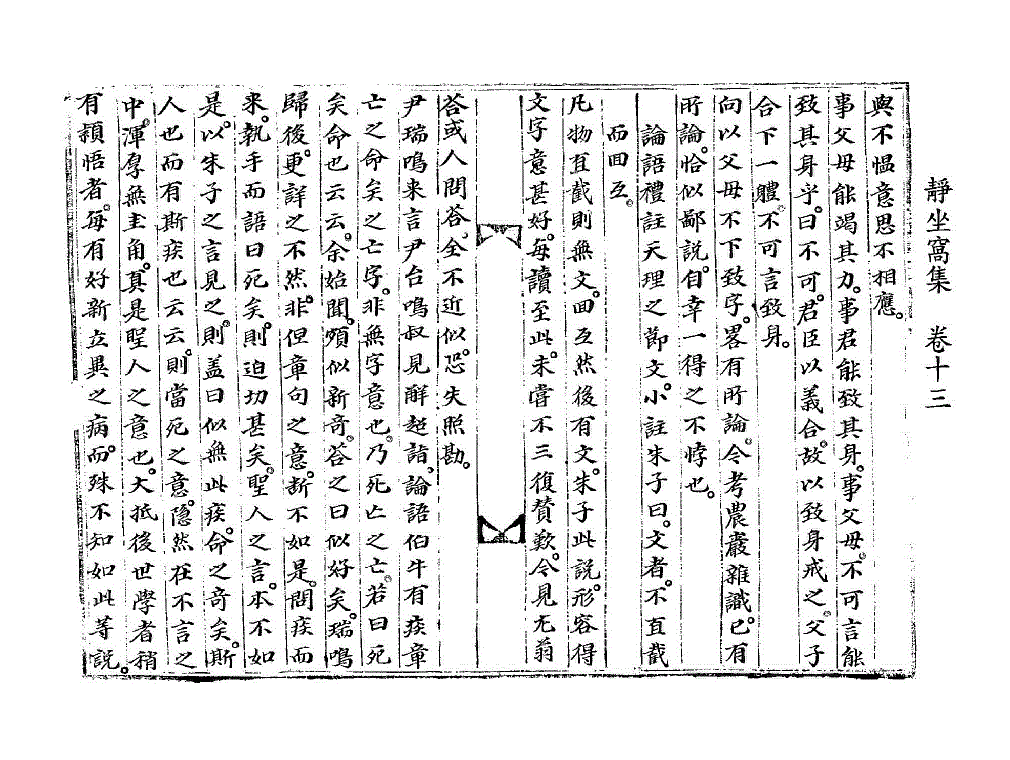 与不愠意思不相应。
与不愠意思不相应。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事父母。不可言能致其身乎。曰不可。君臣以义合。故以致身戒之。父子合下一体。不可言致身。
向以父母不下致字。略有所论。今考农岩杂识。已有所论。恰似鄙说。自幸一得之不悖也。
论语礼注天理之节文。小注朱子曰。文者。不直截而回互。
凡物直截则无文。回互然后有文。朱子此说。形容得文字意甚好。每读至此。未尝不三复赞叹。今见尤翁答或人问答。全不近似。恐失照勘。
尹瑞鸣来言尹台鸣叔见解超诣。论语伯牛有疾章亡之命矣之亡字。非无字意也。乃死亡之亡。若曰死矣命也云云。余始闻。颇似新奇。答之曰似好矣。瑞鸣归后。更详之不然。非但章句之意。断不如是。问疾而来。执手而语曰死矣。则迫切甚矣。圣人之言。本不如是。以朱子之言见之。则盖曰似无此疾。命之奇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云云。则当死之意。隐然在不言之中。浑厚无圭角。真是圣人之意也。大抵后世学者稍有颖悟者。每有好新立异之病。而殊不知如此等说。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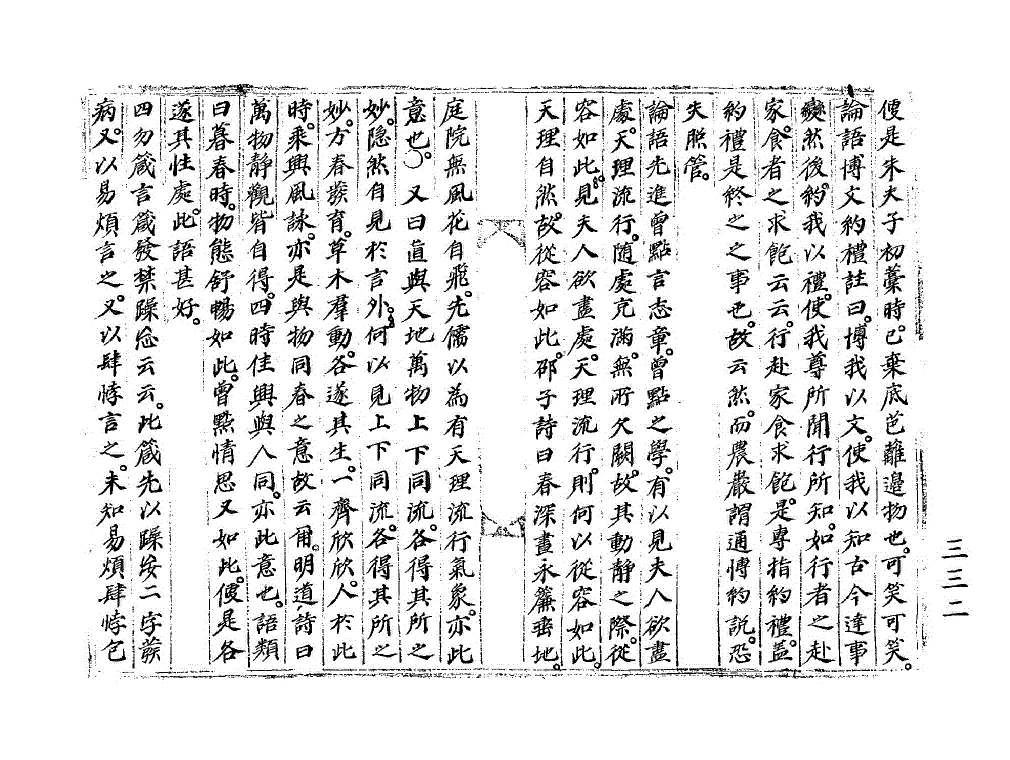 便是朱夫子初藁时。已弃底芭蓠边物也。可笑可笑。
便是朱夫子初藁时。已弃底芭蓠边物也。可笑可笑。论语博文约礼注曰。博我以文。使我以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云云。行赴家食求饱。是专指约礼。盖约礼是终之之事也。故云然。而农岩谓通博约说。恐失照管。
论语先进曾点言志章。曾点之学。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所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则何以从容如此。天理自然。故从容如此。邵子诗曰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先儒以为有天理流行气象。亦此意也。○又曰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何以见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方春发育。草木群动。各遂其生。一齐欣欣。人于此时。乘兴风咏。亦是与物同春之意故云尔。明道诗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亦此意也。语类曰暮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处。此语甚好。
四勿箴言箴发禁躁忘云云。此箴先以躁妄二字发病。又以易烦言之。又以肆悖言之。未知易烦肆悖包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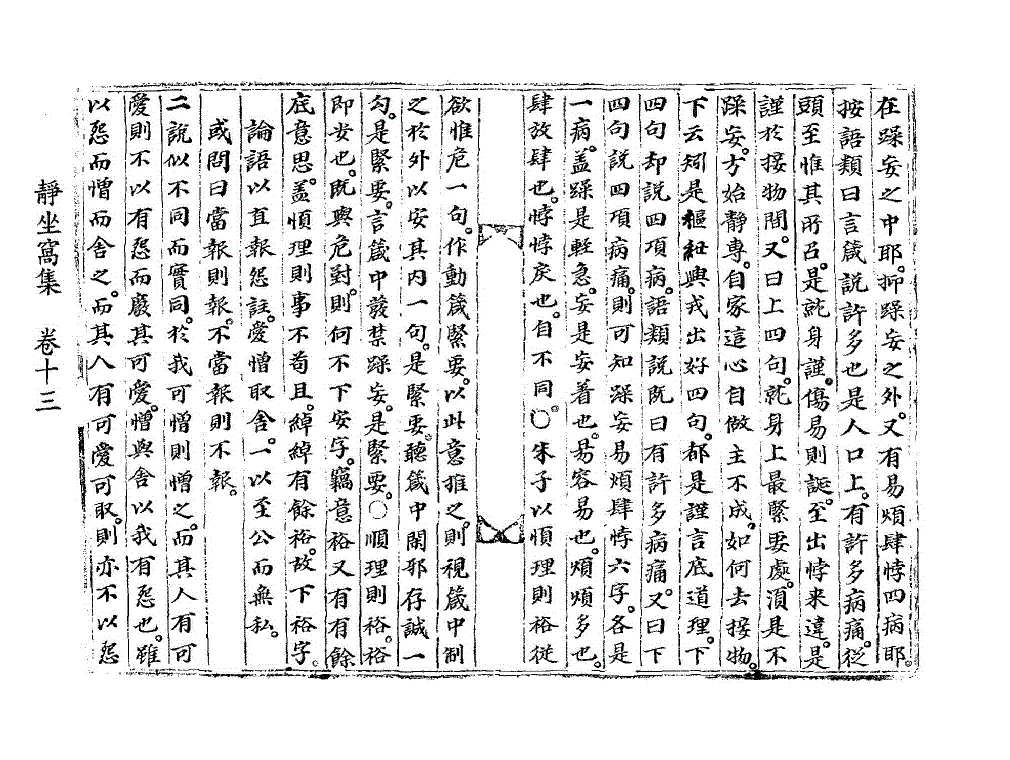 在躁妄之中耶。抑躁妄之外。又有易烦肆悖四病耶。按语类曰言箴说许多也是人口上。有许多病痛。从头至惟其所召。是就身谨。伤易则诞。至出悖来违。是谨于接物间。又曰上四句。就身上最紧要处。须是不躁妄。方始静专。自家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枢纽兴戎出好四句。都是谨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说四项病。语类说既曰有许多病痛。又曰下四句说四项病痛。则可知躁妄易烦肆悖六字。各是一病。盖躁是轻急。妄是妄着也。易容易也。烦烦多也。肆放肆也。悖悖戾也。自不同。○朱子以㥧理则裕从欲惟危一句。作动箴紧要。以此意推之。则视箴中制之于外以安其内一句。是紧要。听箴中闲邪存诚一勾。是紧要。言箴中发禁躁妄。是紧要。○顺理则裕。裕即安也。既与危对。则何不下安字。窃意裕又有有馀底意思。盖㥧理则事不苟且。绰绰有馀裕。故下裕字。
在躁妄之中耶。抑躁妄之外。又有易烦肆悖四病耶。按语类曰言箴说许多也是人口上。有许多病痛。从头至惟其所召。是就身谨。伤易则诞。至出悖来违。是谨于接物间。又曰上四句。就身上最紧要处。须是不躁妄。方始静专。自家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枢纽兴戎出好四句。都是谨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说四项病。语类说既曰有许多病痛。又曰下四句说四项病痛。则可知躁妄易烦肆悖六字。各是一病。盖躁是轻急。妄是妄着也。易容易也。烦烦多也。肆放肆也。悖悖戾也。自不同。○朱子以㥧理则裕从欲惟危一句。作动箴紧要。以此意推之。则视箴中制之于外以安其内一句。是紧要。听箴中闲邪存诚一勾。是紧要。言箴中发禁躁妄。是紧要。○顺理则裕。裕即安也。既与危对。则何不下安字。窃意裕又有有馀底意思。盖㥧理则事不苟且。绰绰有馀裕。故下裕字。论语以直报怨注。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
或问曰当报则报。不当报则不报。
二说似不同而实同。于我可憎则憎之。而其人有可爱则不以有怨而废其可爱。憎与舍以我有怨也。虽以怨而憎而舍之。而其人有可爱可取。则亦不以怨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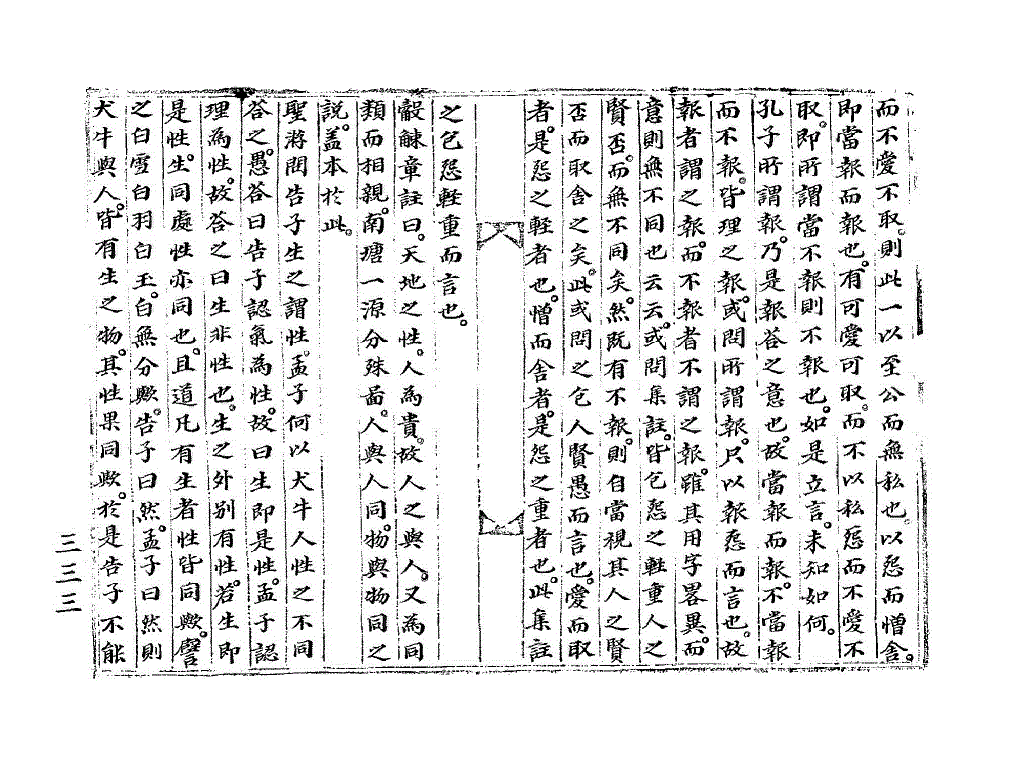 而不爱不取。则此一以至公而无私也。以怨而憎舍。即当报而报也。有可爱可取。而不以私怨而不爱不取。即所谓当不报则不报也。如是立言。未知如何。
而不爱不取。则此一以至公而无私也。以怨而憎舍。即当报而报也。有可爱可取。而不以私怨而不爱不取。即所谓当不报则不报也。如是立言。未知如何。孔子所谓报。乃是报答之意也。故当报而报。不当报而不报。皆理之报。或问所谓报。只以报怨而言也。故报者谓之报。而不报者不谓之报。虽其用字略异。而意则无不同也云云。或问集注。皆包怨之轻重人之贤否。而无不同矣。然既有不报。则自当视其人之贤否而取舍之矣。此或问之包人贤愚而言也。爱而取者。是怨之轻者也。憎而舍者。是怨之重者也。此集注之包怨轻重而言也。
觳觫章注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人之与人。又为同类而相亲。南塘一源分殊啚。人与人同。物与物同之说。盖本于此。
圣游问告子生之谓性。孟子何以犬牛人性之不同答之。愚答曰告子认气为性。故曰生即是性。孟子认理为性。故答之曰生非性也。生之外别有性。若生即是性。生同处性亦同也。且道凡有生者性皆同欤。譬之白雪白羽白玉。白无分欤。告子曰然。孟子曰然则犬牛与人。皆有生之物。其性果同欤。于是告子不能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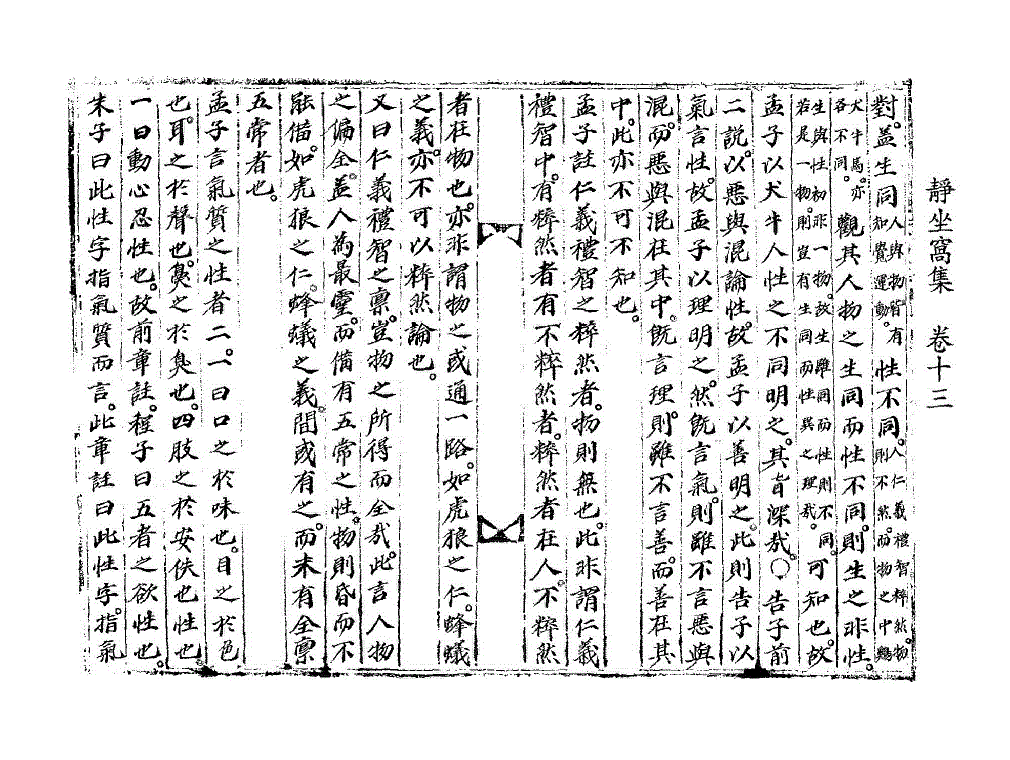 对。盖生同(人与物皆有知觉运动。)性不同。(人仁义礼智粹然。物则不然。而物之中鸡犬牛马。亦各不同。)观其人物之生同而性不同。则生之非性。(生与性初非一物。故生虽同而性则不同。若是一物。则岂有生同而性异之理哉。)可知也。故孟子以犬牛人性之不同明之。其旨深哉。○告子前二说。以恶与混论性。故孟子以善明之。此则告子以气言性。故孟子以理明之。然既言气。则虽不言恶与混。而恶与混在其中。既言理。则虽不言善。而善在其中。此亦不可不知也。
对。盖生同(人与物皆有知觉运动。)性不同。(人仁义礼智粹然。物则不然。而物之中鸡犬牛马。亦各不同。)观其人物之生同而性不同。则生之非性。(生与性初非一物。故生虽同而性则不同。若是一物。则岂有生同而性异之理哉。)可知也。故孟子以犬牛人性之不同明之。其旨深哉。○告子前二说。以恶与混论性。故孟子以善明之。此则告子以气言性。故孟子以理明之。然既言气。则虽不言恶与混。而恶与混在其中。既言理。则虽不言善。而善在其中。此亦不可不知也。孟子注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此非谓仁义礼智中。有粹然者有不粹然者。粹然者在人。不粹然者在物也。亦非谓物之或通一路。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亦不可以粹然论也。
又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言人物之偏全。盖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物则昏而不能备。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间或有之。而未有全禀五常者也。
孟子言气质之性者二。一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一曰动心忍性也。故前章注。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朱子曰此性字指气质而言。此章注曰此性字。指气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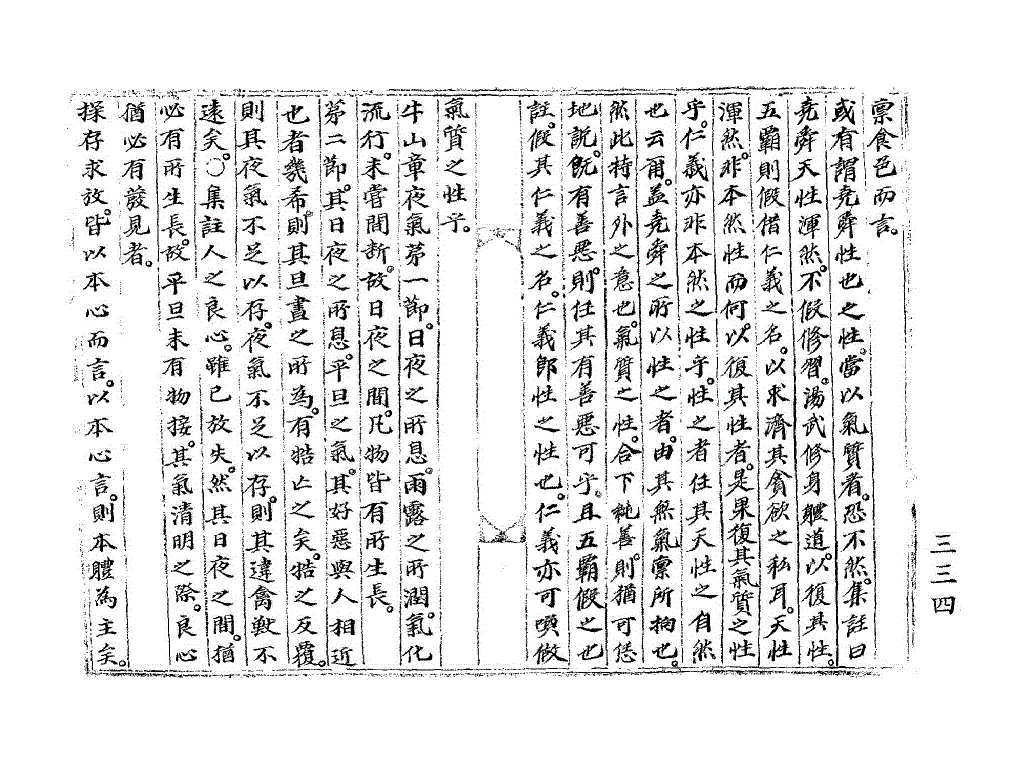 禀食色而言。
禀食色而言。或有谓尧舜性也之性。当以气质看。恐不然。集注曰尧舜天性浑然。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天性浑然。非本然性而何。以复其性者。是果复其气质之性乎。仁义亦非本然之性乎。性之者任其天性之自然也云尔。盖尧舜之所以性之者。由其无气禀所拘也。然此特言外之意也。气质之性。合下纯善。则犹可恁地说。既有善恶。则任其有善恶可乎。且五霸假之也注。假其仁义之名。仁义即性之性也。仁义亦可唤做气质之性乎。
牛山章夜气第一节。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气化流行。未尝间断。故日夜之间。凡物皆有所生长。
第二节。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矣。牿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集注人之良心。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间。犹必有所生长。故平旦未有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
操存求放。皆以本心而言。以本心言。则本体为主矣。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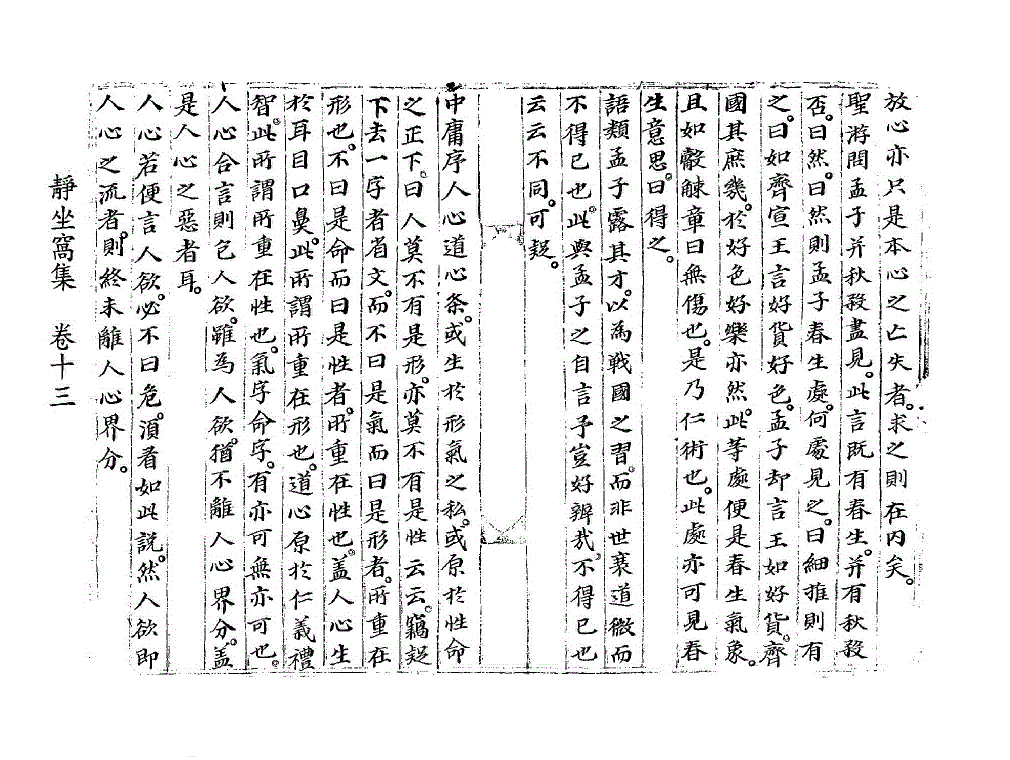 放心亦只是本心之亡失者。求之则在内矣。
放心亦只是本心之亡失者。求之则在内矣。圣游问孟子并秋杀尽见。此言既有春生。并有秋杀否。曰然。曰然则孟子春生处。何处见之。曰细推则有之。曰如齐宣王言好货好色。孟子却言王如好货。齐国其庶几。于好色好乐亦然。此等处便是春生气象。且如觳觫章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此处亦可见春生意思。曰得之。
语类孟子露其才。以为战国之习。而非世衰道微而不得已也。此与孟子之自言予岂好辨哉。不得已也云云不同。可疑。
中庸序人心道心条。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下。曰人莫不有是形。亦莫不有是性云云。窃疑下去一字者省文。而不曰是气而曰是形者。所重在形也。不曰是命而曰是性者。所重在性也。盖人心生于耳目口鼻。此所谓所重在形也。道心原于仁义礼智。此所谓所重在性也。气字命字。有亦可无亦可也。
人心合言则包人欲。虽为人欲。犹不离人心界分。盖是人心之恶者耳。
人心若便言人欲。必不曰危。须看如此说。然人欲即人心之流者。则终未离人心界分。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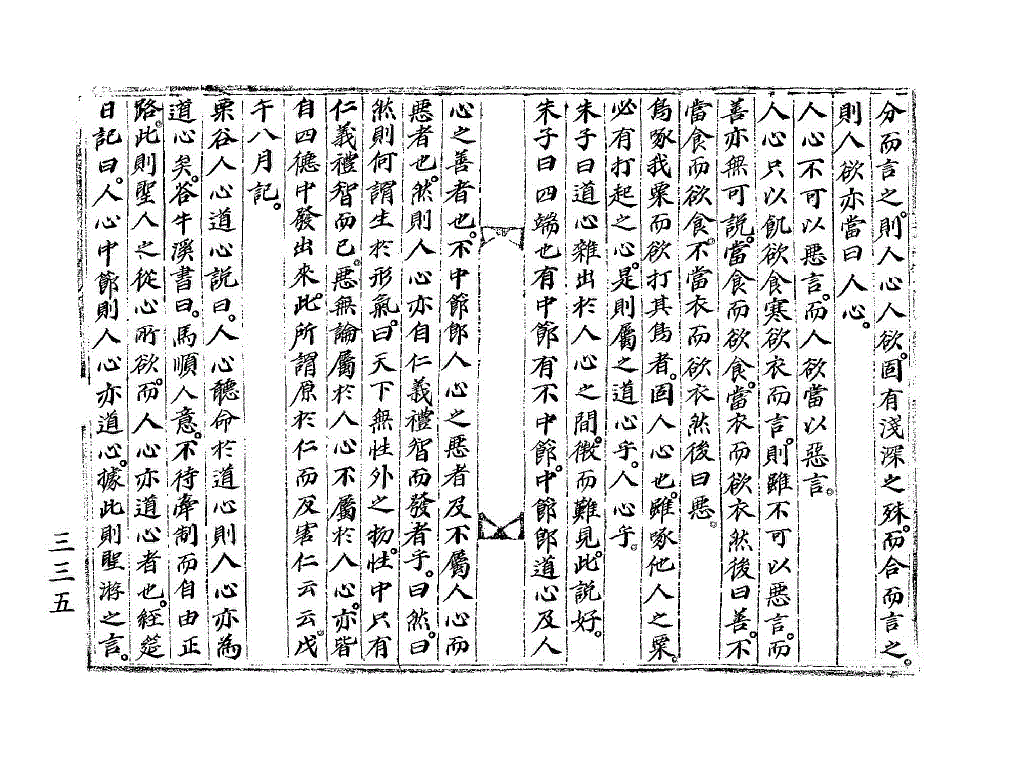 分而言之。则人心人欲。固有浅深之殊。而合而言之。则人欲亦当曰人心。
分而言之。则人心人欲。固有浅深之殊。而合而言之。则人欲亦当曰人心。人心不可以恶言。而人欲当以恶言。
人心只以饥欲食寒欲衣而言。则虽不可以恶言。而善亦无可说。当食而欲食。当衣而欲衣然后曰善。不当食而欲食。不当衣而欲衣然后曰恶。
鸟啄我粟而欲打其鸟者。固人心也。虽啄他人之粟。必有打起之心。是则属之道心乎。人心乎。
朱子曰道心杂出于人心之间。微而难见。此说好。
朱子曰四端也有中节有不中节。中节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不中节即人心之恶者及不属人心而恶者也。然则人心亦自仁义礼智而发者乎。曰然。曰然则何谓生于形气。曰天下无性外之物。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已。恶无论属于人心不属于人心。亦皆自四德中发出来。此所谓原于仁而反害仁云云。戊午八月记。
栗谷人心道心说曰。人心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亦为道心矣。答牛溪书曰。马顺人意。不待牵制而自由正路。此则圣人之从心所欲。而人心亦道心者也。经筵日记曰。人心中节则人心亦道心。据此则圣游之言。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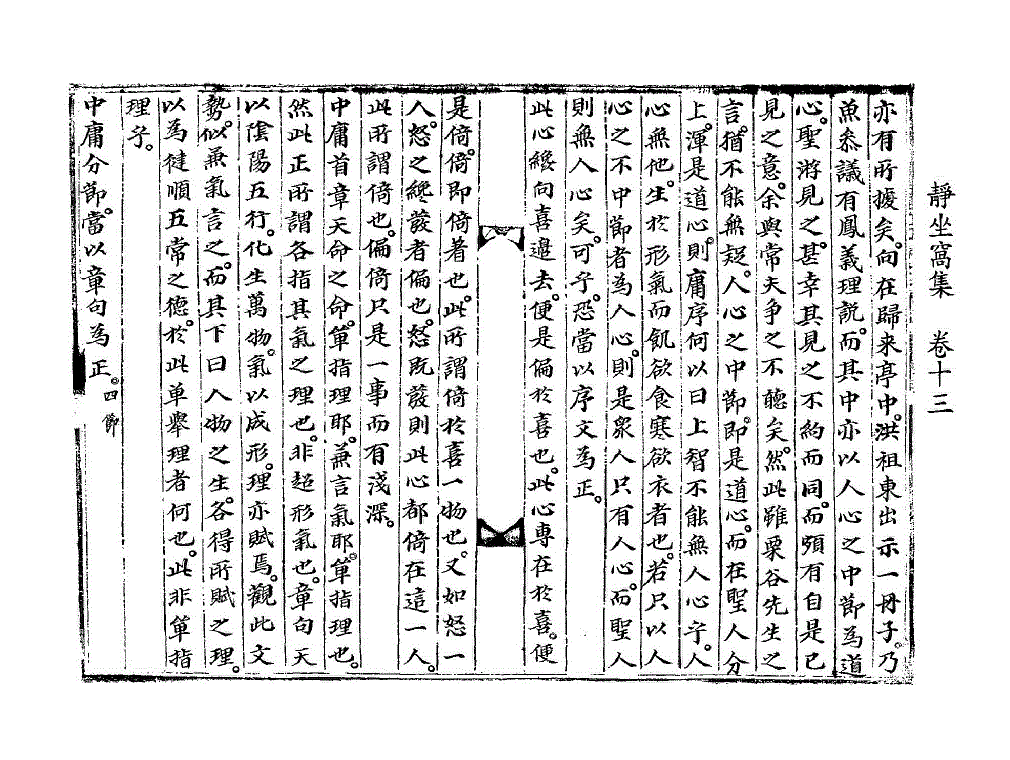 亦有所据矣。向在归来亭中。洪祖东出示一册子。乃鱼参议有凤义理说。而其中亦以人心之中节为道心。圣游见之。甚幸其见之不约而同。而颇有自是己见之意。余与常夫争之不听矣。然此虽栗谷先生之言。犹不能无疑。人心之中节。即是道心。而在圣人分上。浑是道心。则庸序何以曰上智不能无人心乎。人心无他。生于形气而饥欲食寒欲衣者也。若只以人心之不中节者为人心。则是众人只有人心。而圣人则无人心矣。可乎。恐当以序文为正。
亦有所据矣。向在归来亭中。洪祖东出示一册子。乃鱼参议有凤义理说。而其中亦以人心之中节为道心。圣游见之。甚幸其见之不约而同。而颇有自是己见之意。余与常夫争之不听矣。然此虽栗谷先生之言。犹不能无疑。人心之中节。即是道心。而在圣人分上。浑是道心。则庸序何以曰上智不能无人心乎。人心无他。生于形气而饥欲食寒欲衣者也。若只以人心之不中节者为人心。则是众人只有人心。而圣人则无人心矣。可乎。恐当以序文为正。此心才向喜边去。便是偏于喜也。此心专在于喜。便是倚。倚即倚着也。此所谓倚于喜一物也。又如怒一人。怒之才发者偏也。怒既发则此心都倚在这一人。此所谓倚也。偏倚只是一事而有浅深。
中庸首章天命之命。单指理耶。兼言气耶。单指理也。然此正所谓各指其气之理也。非超形气也。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观此文势。似兼气言之。而其下曰人物之生。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于此单举理者何也。此非单指理乎。
中庸分节。当以章句为正。(四节)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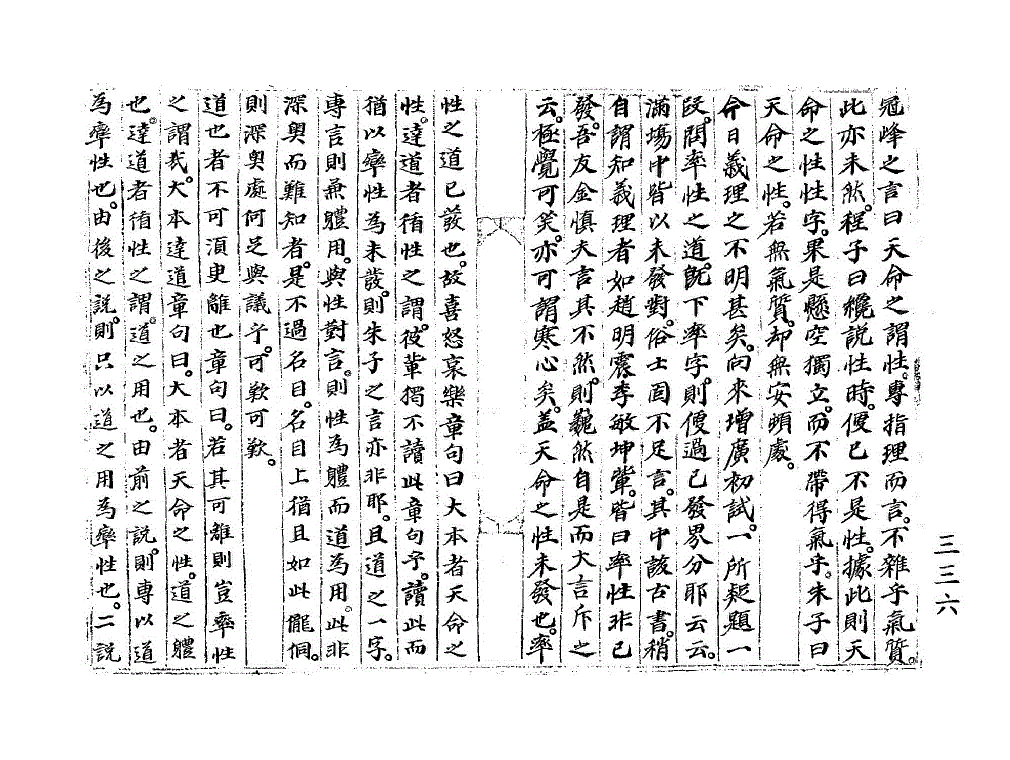 冠峰之言曰天命之谓性。专指理而言。不杂乎气质。此亦未然。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据此则天命之性性字。果是悬空独立。而不带得气乎。朱子曰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
冠峰之言曰天命之谓性。专指理而言。不杂乎气质。此亦未然。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据此则天命之性性字。果是悬空独立。而不带得气乎。朱子曰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今日义理之不明甚矣。向来增广初试。一所疑题一段。问率性之道。既下率字。则便过已发界分耶云云。满场中皆以未发对。俗士固不足言。其中该古书。稍自谓知义理者如赵明震,李敏坤辈。皆曰率性非已发。吾友金慎夫言其不然。则巍然自是而大言斥之云。极觉可笑。亦可谓寒心矣。盖天命之性未发也。率性之道已发也。故喜怒哀乐章句曰大本者天命之性。达道者循性之谓。彼辈独不读此章句乎。读此而犹以率性为未发。则朱子之言亦非耶。且道之一字。专言则兼体用。与性对言。则性为体而道为用。此非深奥而难知者。是不过名目。名目上犹且如此儱侗。则深奥处何足与议乎。可叹可叹。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章句曰。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大本达道章句曰。大本者天命之性。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道之用也。由前之说。则专以道为率性也。由后之说。则只以道之用为率性也。二说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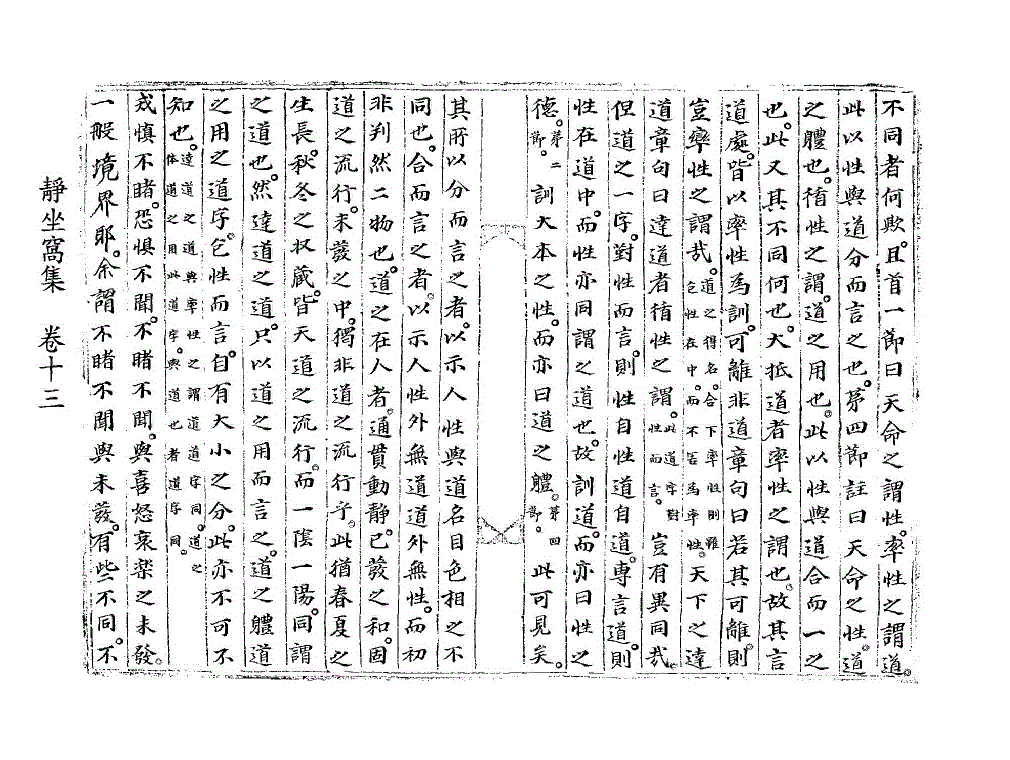 不同者何欤。且首一节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以性与道分而言之也。第四节注曰天命之性。道之体也。循性之谓。道之用也。此以性与道合而一之也。此又其不同何也。大抵道者率性之谓也。故其言道处。皆以率性为训。可离非道章句曰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道之得名。合下率性则虽包性在中。而不害为率性。)天下之达道章句曰达道者循性之谓。(此道字对性而言。)岂有异同哉。但道之一字。对性而言。则性自性道自道。专言道。则性在道中。而性亦同谓之道也。故训道。而亦曰性之德。(第二节。)训大本之性。而亦曰道之体。(第四节。)此可见矣。其所以分而言之者。以示人性与道名目色相之不同也。合而言之者。以示人性外无道道外无性。而初非判然二物也。道之在人者。通贯动静。已发之和。固道之流行。未发之中。独非道之流行乎。此犹春夏之生长。秋冬之收藏。皆天道之流行。而一阴一阳。同谓之道也。然达道之道。只以道之用而言之。道之体道之用之道字。包性而言。自有大小之分。此亦不可不知也。(达道之道与率性之谓道道字同。道之体道之用此道字。与道也者道字同。)
不同者何欤。且首一节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以性与道分而言之也。第四节注曰天命之性。道之体也。循性之谓。道之用也。此以性与道合而一之也。此又其不同何也。大抵道者率性之谓也。故其言道处。皆以率性为训。可离非道章句曰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道之得名。合下率性则虽包性在中。而不害为率性。)天下之达道章句曰达道者循性之谓。(此道字对性而言。)岂有异同哉。但道之一字。对性而言。则性自性道自道。专言道。则性在道中。而性亦同谓之道也。故训道。而亦曰性之德。(第二节。)训大本之性。而亦曰道之体。(第四节。)此可见矣。其所以分而言之者。以示人性与道名目色相之不同也。合而言之者。以示人性外无道道外无性。而初非判然二物也。道之在人者。通贯动静。已发之和。固道之流行。未发之中。独非道之流行乎。此犹春夏之生长。秋冬之收藏。皆天道之流行。而一阴一阳。同谓之道也。然达道之道。只以道之用而言之。道之体道之用之道字。包性而言。自有大小之分。此亦不可不知也。(达道之道与率性之谓道道字同。道之体道之用此道字。与道也者道字同。)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不睹不闻。与喜怒哀乐之未发。一般境界耶。余谓不睹不闻与未发。有些不同。不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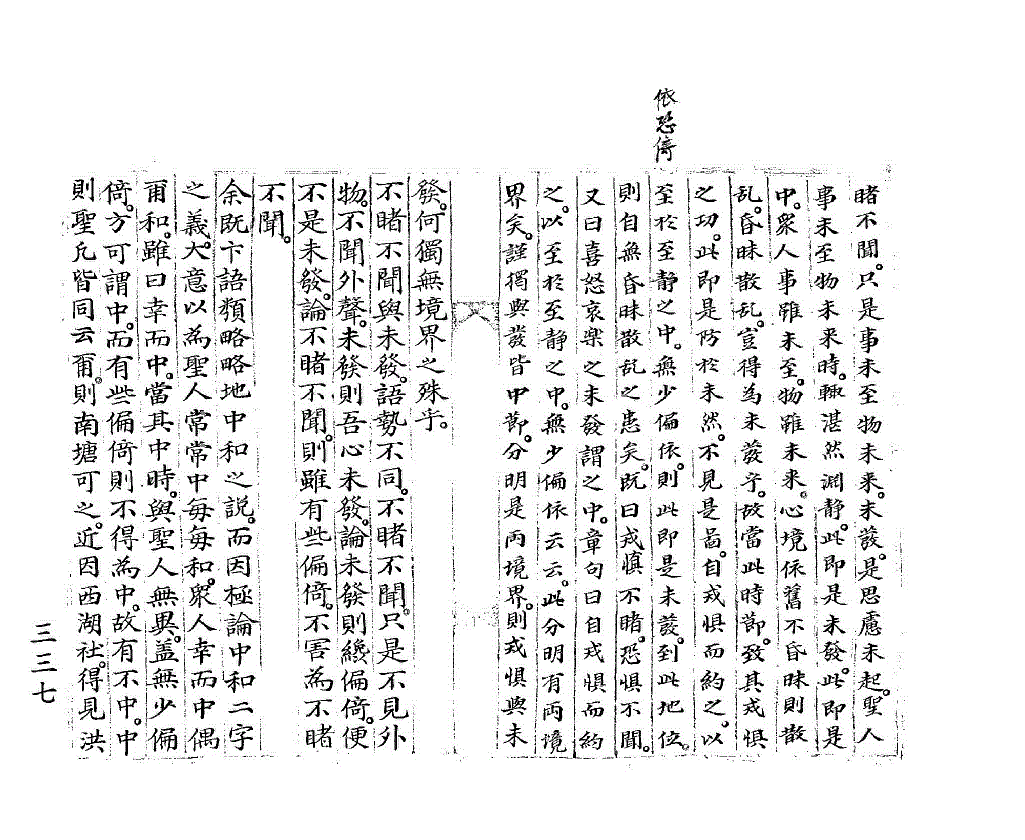 睹不闻。只是事未至物未来。未发。是思虑未起。圣人事未至物未来时。辄湛然渊静。此即是未发。此即是中。众人事虽未至。物虽未来。心境依旧不昏昧则散乱。昏昧散乱。岂得为未发乎。故当此时节。致其戒惧之功。此即是防于未然。不见是啚。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依(依。恐倚。)。则此即是未发。到此地位。则自无昏昧散乱之患矣。既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章句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依云云。此分明有两境界矣。谨独与发皆中节。分明是两境界。则戒惧与未发。何独无境界之殊乎。
睹不闻。只是事未至物未来。未发。是思虑未起。圣人事未至物未来时。辄湛然渊静。此即是未发。此即是中。众人事虽未至。物虽未来。心境依旧不昏昧则散乱。昏昧散乱。岂得为未发乎。故当此时节。致其戒惧之功。此即是防于未然。不见是啚。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依(依。恐倚。)。则此即是未发。到此地位。则自无昏昧散乱之患矣。既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章句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依云云。此分明有两境界矣。谨独与发皆中节。分明是两境界。则戒惧与未发。何独无境界之殊乎。不睹不闻与未发。语势不同。不睹不闻。只是不见外物。不闻外声。未发则吾心未发。论未发则才偏倚。便不是未发。论不睹不闻。则虽有些偏倚。不害为不睹不闻。
余既卞语类略略地中和之说。而因极论中和二字之义。大意以为圣人常常中每每和。众人幸而中偶尔和。虽曰幸而中。当其中时。与圣人无异。盖无少偏倚。方可谓中。而有些偏倚则不得为中。故有不中。中则圣凡皆同云尔。则南塘可之。近因西湖社。得见洪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8H 页
 士东疑目。则有不睹不闻与喜怒哀乐之未发同异之问。余谓语静则有至静未至静。语中则无十分中八九分中。不睹不闻。只是事未至物未来。不得为至静。未发。是不偏不倚。方是至静。分明是两境界云尔。则常夫信之。圣游疑之。余潜思累日。不知吾说之为非。而且考中庸或问。论戒惧谨独。而曰此以由教而入者。其始当如此。学者当无须臾毫忽之不谨而周防之。其论致中和位育。而曰自其不睹不闻之前。而所以戒谨恐惧者。愈严愈敬。以至于无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则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得此然后益信一得之不悖也。盖未发非不是不睹不闻。而只言不睹不闻。则包不得未发意思。形容不到至静境界。圣人非不戒惧。而圣人戒惧。戒惧之严敬者也。故戒惧章句。则曰虽不闻见。亦不敢忽。此可见学者事也。致中和。或问则曰所以戒谨恐惧者。愈严愈敬。(此章句约字意。)此可见圣人事也。向吾所谓两境界者非耶。○又按农岩集。答遂翁书曰虽非圣人。亦须有不睹不闻时节。但不能敬而存之。则方寸之中。未免有偏倚而不得为至静矣。然则不睹不闻。只是事物未接时。非此心至静境界也。○中庸戒惧谨
士东疑目。则有不睹不闻与喜怒哀乐之未发同异之问。余谓语静则有至静未至静。语中则无十分中八九分中。不睹不闻。只是事未至物未来。不得为至静。未发。是不偏不倚。方是至静。分明是两境界云尔。则常夫信之。圣游疑之。余潜思累日。不知吾说之为非。而且考中庸或问。论戒惧谨独。而曰此以由教而入者。其始当如此。学者当无须臾毫忽之不谨而周防之。其论致中和位育。而曰自其不睹不闻之前。而所以戒谨恐惧者。愈严愈敬。以至于无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则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得此然后益信一得之不悖也。盖未发非不是不睹不闻。而只言不睹不闻。则包不得未发意思。形容不到至静境界。圣人非不戒惧。而圣人戒惧。戒惧之严敬者也。故戒惧章句。则曰虽不闻见。亦不敢忽。此可见学者事也。致中和。或问则曰所以戒谨恐惧者。愈严愈敬。(此章句约字意。)此可见圣人事也。向吾所谓两境界者非耶。○又按农岩集。答遂翁书曰虽非圣人。亦须有不睹不闻时节。但不能敬而存之。则方寸之中。未免有偏倚而不得为至静矣。然则不睹不闻。只是事物未接时。非此心至静境界也。○中庸戒惧谨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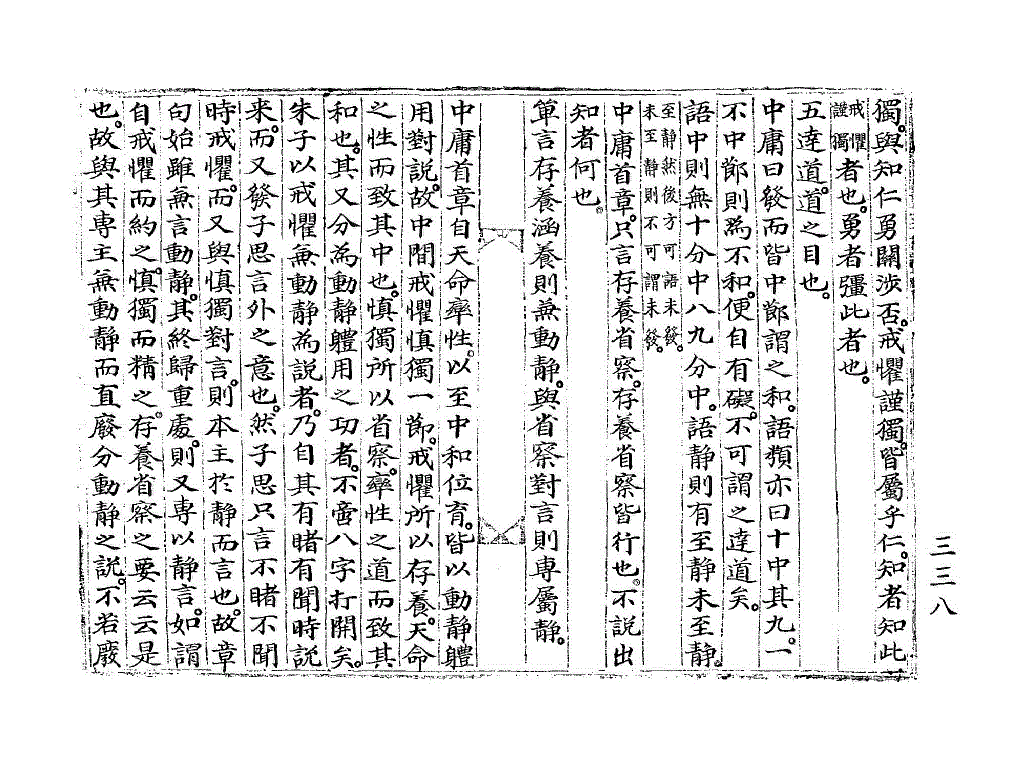 独。与知仁勇关涉否。戒惧谨独。皆属乎仁。知者知此(戒惧谨独)者也。勇者彊此者也。
独。与知仁勇关涉否。戒惧谨独。皆属乎仁。知者知此(戒惧谨独)者也。勇者彊此者也。五达道。道之目也。
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语类亦曰十中其九。一不中节则为不和。便自有碍。不可谓之达道矣。
语中则无十分中八九分中。语静则有至静未至静。(至静然后方可语未发。未至静则不可谓未发。)
中庸首章。只言存养省察。存养省察皆行也。不说出知者何也。
单言存养涵养则兼动静。与省察对言则专属静。
中庸首章自天命率性。以至中和位育。皆以动静体用对说。故中间戒惧慎独一节。戒惧所以存养。天命之性而致其中也。慎独所以省察。率性之道而致其和也。其又分为动静体用之功者。不啻八字打开矣。朱子以戒惧兼动静为说者。乃自其有睹有闻时说来。而又发子思言外之意也。然子思只言不睹不闻时戒惧。而又与慎独对言。则本主于静而言也。故章句始虽兼言动静。其终归重处。则又专以静言。如谓自戒惧而约之。慎独而精之。存养省察之要云云是也。故与其专主兼动静而直废分动静之说。不若废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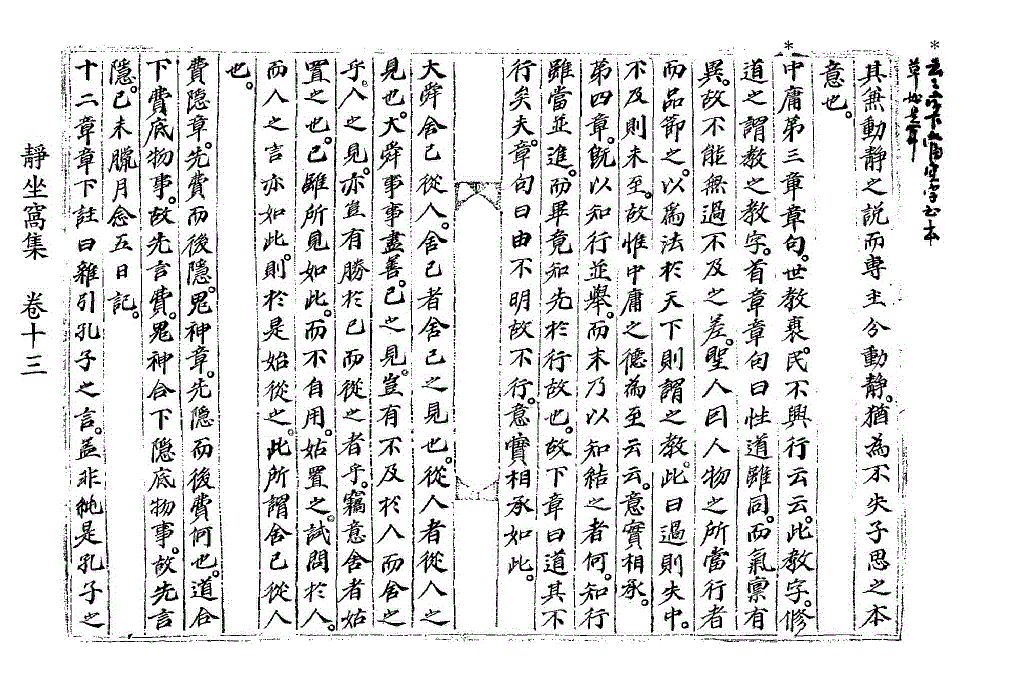 其兼动静之说而专主分动静。犹为不失子思之本意也。
其兼动静之说而专主分动静。犹为不失子思之本意也。中庸第三章章句。世教衰。民不兴行云云(云云字下。当空字书。本草如是耳。)。此教字。修道之谓教之教字。首章章句曰性道虽同。而气禀有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此曰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云云。意实相承。
第四章。既以知行并举。而末乃以知结之者何。知行虽当并进。而毕竟知先于行故也。故下章曰道其不行矣夫。章句曰由不明故不行。意实相承如此。
大舜舍己从人。舍己者舍己之见也。从人者从人之见也。大舜事事尽善。己之见。岂有不及于人而舍之乎。人之见。亦岂有胜于己而从之者乎。窃意舍者姑置之也。己虽所见如此。而不自用。姑置之。试问于人。而人之言亦如此。则于是始从之。此所谓舍己从人也。
费隐章。先费而后隐。鬼神章。先隐而后费何也。道合下费底物事。故先言费。鬼神合下隐底物事。故先言隐。己未腊月念五日记。
十二章章下注曰杂引孔子之言。盖非纯是孔子之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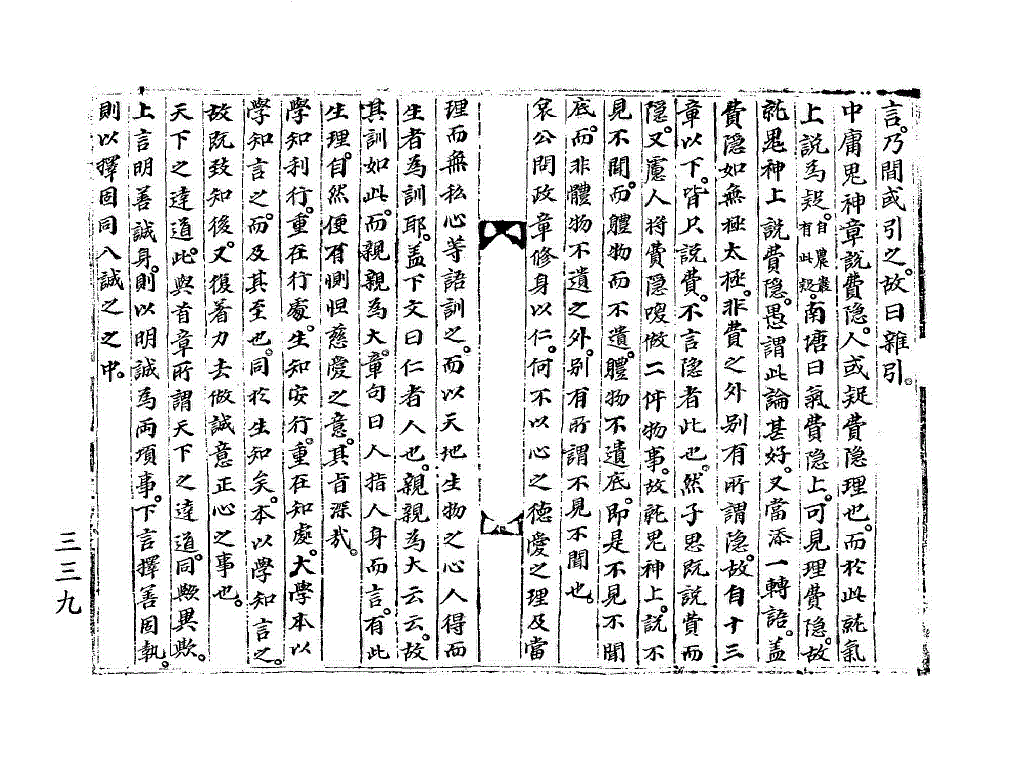 言。乃间或引之。故曰杂引。
言。乃间或引之。故曰杂引。中庸鬼神章说费隐。人或疑费隐理也。而于此就气上说为疑。(自农岩有此疑。)南塘曰气费隐上。可见理费隐。故就鬼神上说费隐。愚谓此论甚好。又当添一转语。盖费隐如无极太极。非费之外别有所谓隐。故自十三章以下。皆只说费。不言隐者此也。然子思既说费而隐。又虑人将费隐唤做二件物事。故就鬼神上。说不见不闻。而体物而不遗。体物不遗底。即是不见不闻底。而非体物不遗之外。别有所谓不见不闻也。
哀公问政章修身以仁。何不以心之德爱之理及当理而无私心等语训之。而以天地生物之心人得而生者为训耶。盖下文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云云。故其训如此。而亲亲为大。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有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其旨深哉。
学知利行。重在行处。生知安行。重在知处。大学本以学知言之。而及其至也。同于生知矣。本以学知言之。故既致知后。又复着力去做诚意正心之事也。
天下之达道。此与首章所谓天下之达道。同欤异欤。
上言明善诚身。则以明诚为两项事。下言择善固执。则以择固同入诚之之中。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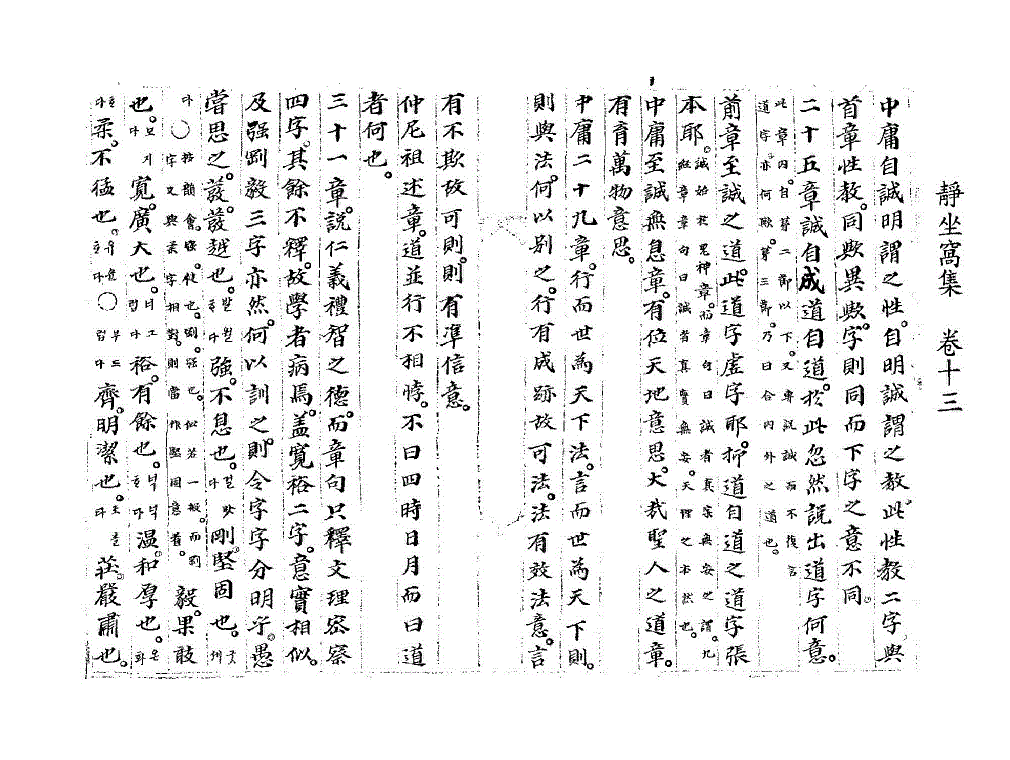 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性教二字。与首章性教。同欤异欤。字则同而下字之意不同。
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性教二字。与首章性教。同欤异欤。字则同而下字之意不同。二十五章诚自成道自道。于此忽然说出道字何意。(此章内。自第二节以下。又专说诚而不复言道字。亦何欤。第三节。乃曰合内外之道也。)
前章至诚之道。此道字虚字耶。抑道自道之道字张本耶。(诚始于鬼神章。而章句曰诚者真宲无妄之谓。九经章章句曰诚者真实无妄。天理之本然也。)
中庸至诚无息章。有位天地意思。大哉圣人之道章。有育万物意思。
中庸二十九章。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则与法。何以别之。行有成迹故可法。法有效法意。言有不欺故可则。则有准信意。
仲尼祖述章。道并行不相悖。不曰四时日月而曰道者何也。
三十一章。说仁义礼智之德。而章句只释文理密察四字。其馀不释。故学者病焉。盖宽裕二字。意实相似。及强刚毅三字亦然。何以训之。则令字字分明乎。愚尝思之。发。发越也。(발월다)强。不息也。(걸다)刚。坚固也。(굿세다○按韵会。强。健也。刚。强也。似若一般。而刚字又与柔字相对。则当作坚固意看。)毅。果敢也。(모지다)宽。广大也。(너그럽다)裕。有馀也。(넉넉다)温。和厚也。(온화다)柔。不猛也。(유슌다○부드럽다)齐。明洁也。(조촐타)庄。严肃也。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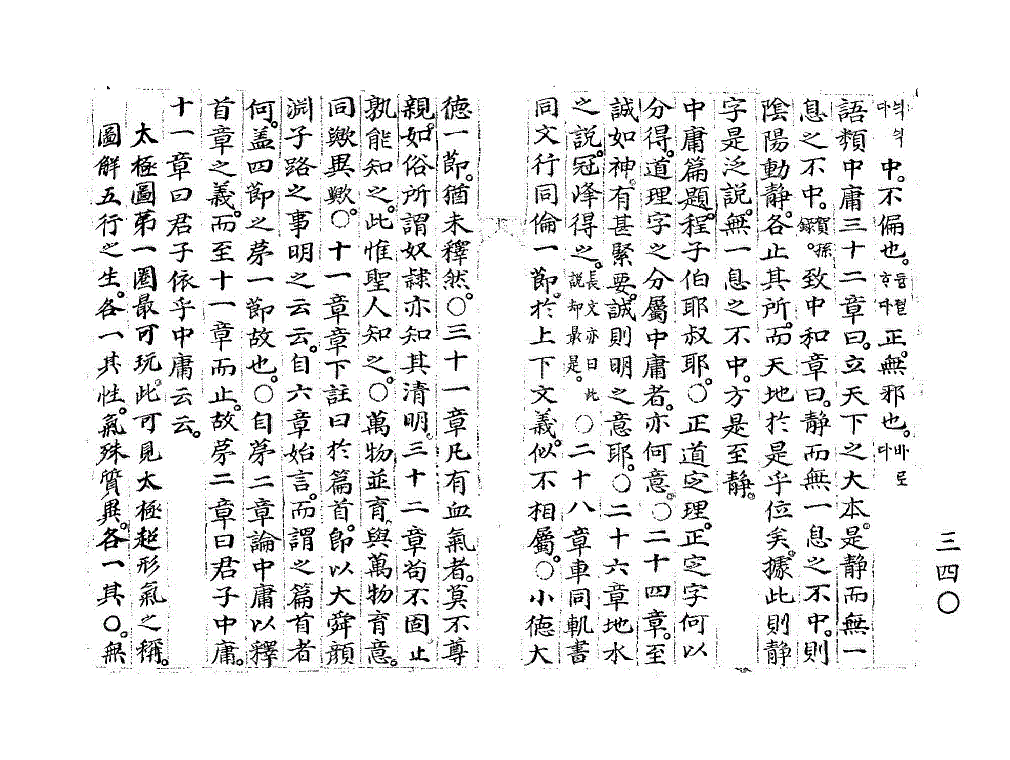 (싁싁다)中。不偏也。(듕졀다)正。无邪也。(바로다)
(싁싁다)中。不偏也。(듕졀다)正。无邪也。(바로다)语类中庸三十二章曰。立天下之大本。是静而无一息之不中。(贺孙录。)致中和章曰。静而无一息之不中。则阴阳动静。各止其所。而天地于是乎位矣。据此则静字是泛说。无一息之不中。方是至静。
中庸篇题。程子伯耶叔耶。○正道定理。正定字何以分得。道理字之分属中庸者。亦何意。○二十四章。至诚如神。有甚紧要。诚则明之意耶。○二十六章地水之说。冠峰得之。(长文亦曰此说却最是。)○二十八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节。于上下文义。似不相属。○小德大德一节。犹未释然。○三十一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如俗所谓奴隶亦知其清明。三十二章苟不固(止)孰能知之。此惟圣人知之。○万物并育。与万物育意。同欤异欤。○十一章章下注曰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云云。自六章始言。而谓之篇首者何。盖四节之第一节故也。○自第二章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而至十一章而止。故第二章曰君子中庸。十一章曰君子依乎中庸云云。
太极图第一圈最可玩。此可见太极超形气之称。图解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〇。无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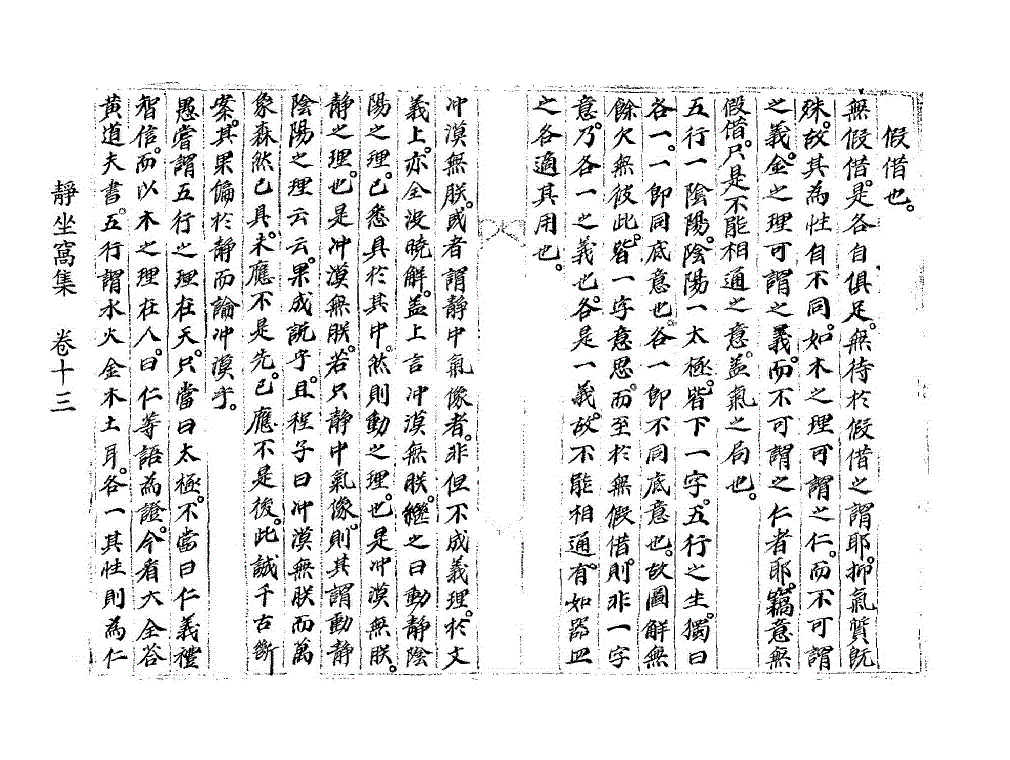 假借也。
假借也。无假借。是各自俱足。无待于假借之谓耶。抑气质既殊。故其为性自不同。如木之理可谓之仁。而不可谓之义。金之理可谓之义。而不可谓之仁者耶。窃意无假借。只是不能相通之意。盖气之局也。
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皆下一字。五行之生。独曰各一。一即同底意也。各一即不同底意也。故图解无馀欠无彼此。皆一字意思。而至于无假借。则非一字意。乃各一之义也。各是一义。故不能相通。有如器皿之各适其用也。
冲漠无朕。或者谓静中气像者。非但不成义理。于文义上。亦全没晓解。盖上言冲漠无朕。继之曰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然则动之理。也是冲漠无朕。静之理。也是冲漠无朕。若只静中气像。则其谓动静阴阳之理云云。果成说乎。且程子曰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此诚千古断案。其果偏于静而论冲漠乎。
愚尝谓五行之理在天。只当曰太极。不当曰仁义礼智信。而以木之理在人。曰仁等语为證。今看大全答黄道夫书。五行谓水火金木土耳。各一其性则为仁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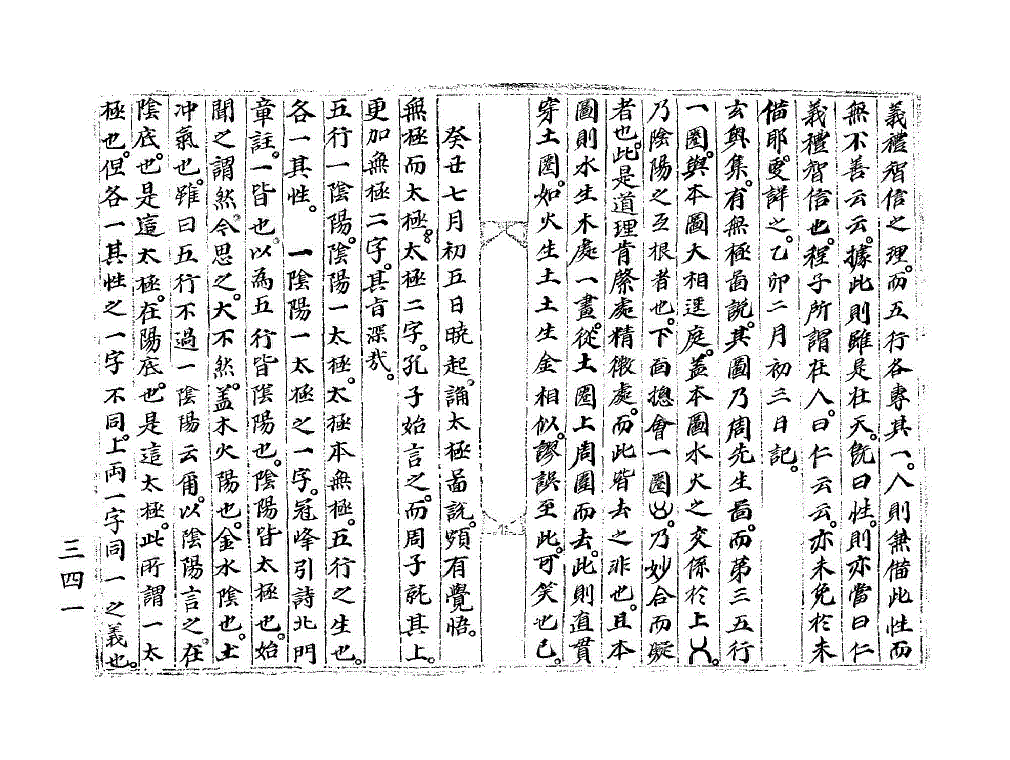 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则兼备此性而无不善云云。据此则虽是在天。既曰性。则亦当曰仁义礼智信也。程子所谓在人。曰仁云云。亦未免于未备耶。更详之。乙卯二月初三日记。
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则兼备此性而无不善云云。据此则虽是在天。既曰性。则亦当曰仁义礼智信也。程子所谓在人。曰仁云云。亦未免于未备耶。更详之。乙卯二月初三日记。玄奥集。有无极啚说。其图乃周先生啚。而第三五行一圈。与本图大相径庭。盖本图水火之交系于上
癸丑七月初五日晓起。诵太极啚说。颇有觉悟。
无极而太极。太极二字。孔子始言之。而周子就其上。更加无极二字。其旨深哉。
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一阴阳一太极之一字。冠峰引诗北门章注。一皆也。以为五行皆阴阳也。阴阳皆太极也。始闻之谓然。今思之。大不然。盖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土冲气也。虽曰五行不过一阴阳云尔。以阴阳言之。在阴底。也是这太极。在阳底。也是这太极。此所谓一太极也。但各一其性之一字不同。上两一字同一之义也。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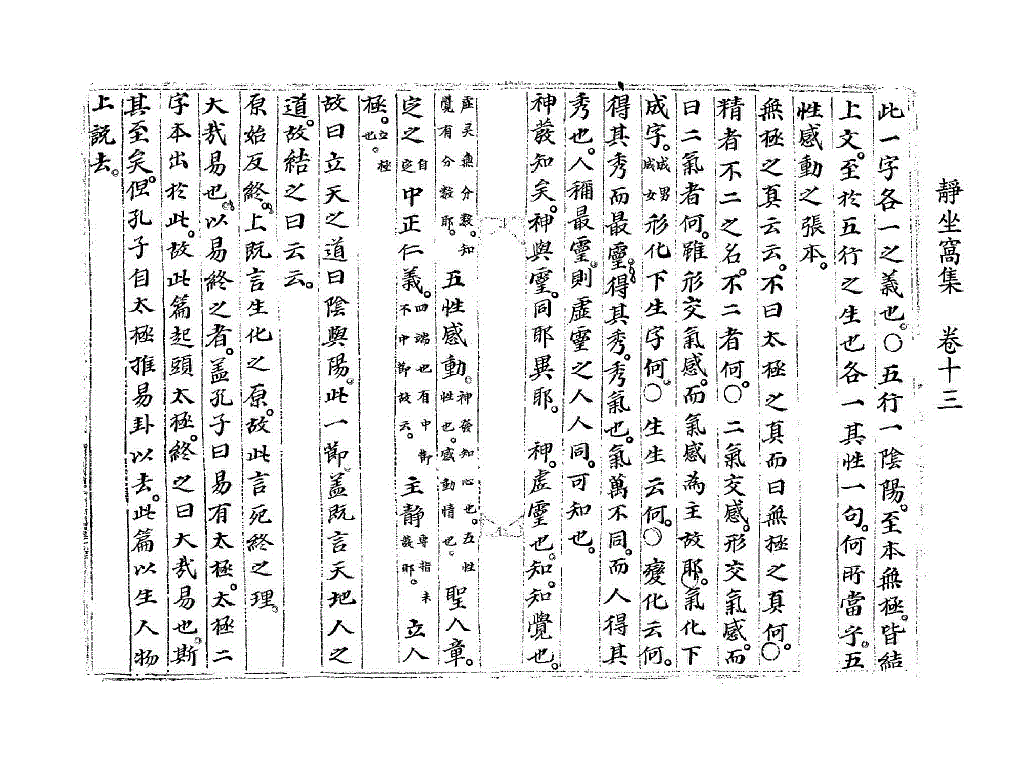 此一字各一之义也。○五行一阴阳。至本无极。皆结上文。至于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一句。何所当乎。五性感动之张本。
此一字各一之义也。○五行一阴阳。至本无极。皆结上文。至于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一句。何所当乎。五性感动之张本。无极之真云云。不曰太极之真而曰无极之真何。○精者不二之名。不二者何。○二气交感。形交气感。而曰二气者何。虽形交气感。而气感为主故耶。○气化下成字。(成男成女)形化下生字何。○生生云何。○变化云何。
得其秀而最灵。得其秀。秀气也。气万不同。而人得其秀也。人称最灵。则虚灵之人人同。可知也。
神发知矣。神与灵。同耶异耶。 神。虚灵也。知。知觉也。(虚灵无分数。知觉有分数耶。)五性感动。(神发知心也。五性性也。感动情也。)圣人章。定之(自定)中正仁义。(四端也有中节不中节故云。)主静(专指未发耶。)立人极。(立极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此一节。盖既言天地人之道。故结之曰云云。
原始反终。上既言生化之原。故此言死终之理。
大哉易也。以易终之者。盖孔子曰易有太极。太极二字本出于此。故此篇起头太极。终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但孔子自太极推易卦以去。此篇以生人物上说去。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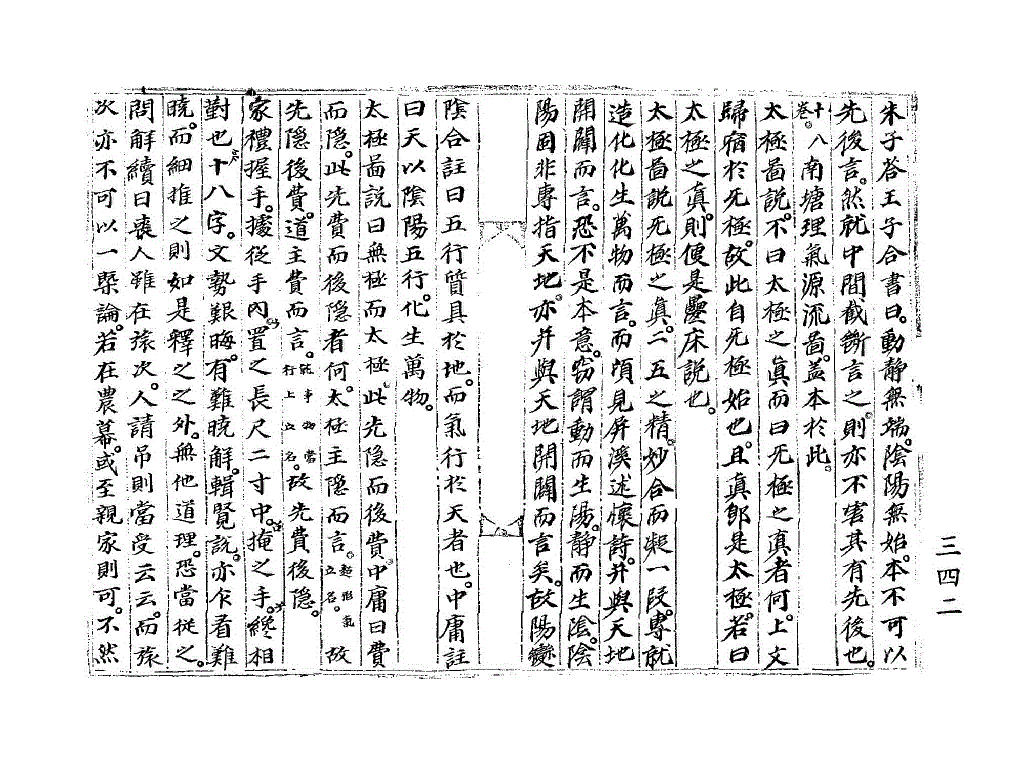 朱子答王子合书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本不可以先后言。然就中间截断言之。则亦不害其有先后也。(十八卷。)南塘理气源流啚。盖本于此。
朱子答王子合书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本不可以先后言。然就中间截断言之。则亦不害其有先后也。(十八卷。)南塘理气源流啚。盖本于此。太极啚说。不曰太极之真而曰无极之真者何。上文归宿于无极。故此自无极始也。且真即是太极。若曰太极之真。则便是叠床说也。
太极啚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一段。专就造化化生万物而言。而顷见屏溪述怀诗。并与天地开辟而言。恐不是本意。窃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固非专指天地。亦并与天地开辟而言矣。故阳变阴合注曰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中庸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
太极啚说曰无极而太极。此先隐而后费。中庸曰费而隐。此先费而后隐者何。太极主隐而言。(超形气立名。)故先隐后费。道主费而言。(就事物当行上立名。)故先费后隐。
家礼握手。据从手内()。置之长尺二寸中()。掩之手()。才相对也()十八字。文势艰晦。有难晓解。辑览说。亦乍看难晓。而细推之则如是释之之外。无他道理。恐当从之。
问解续曰丧人虽在旅次。人请吊则当受云云。而旅次亦不可以一槩论。若在农幕。或至亲家则可。不然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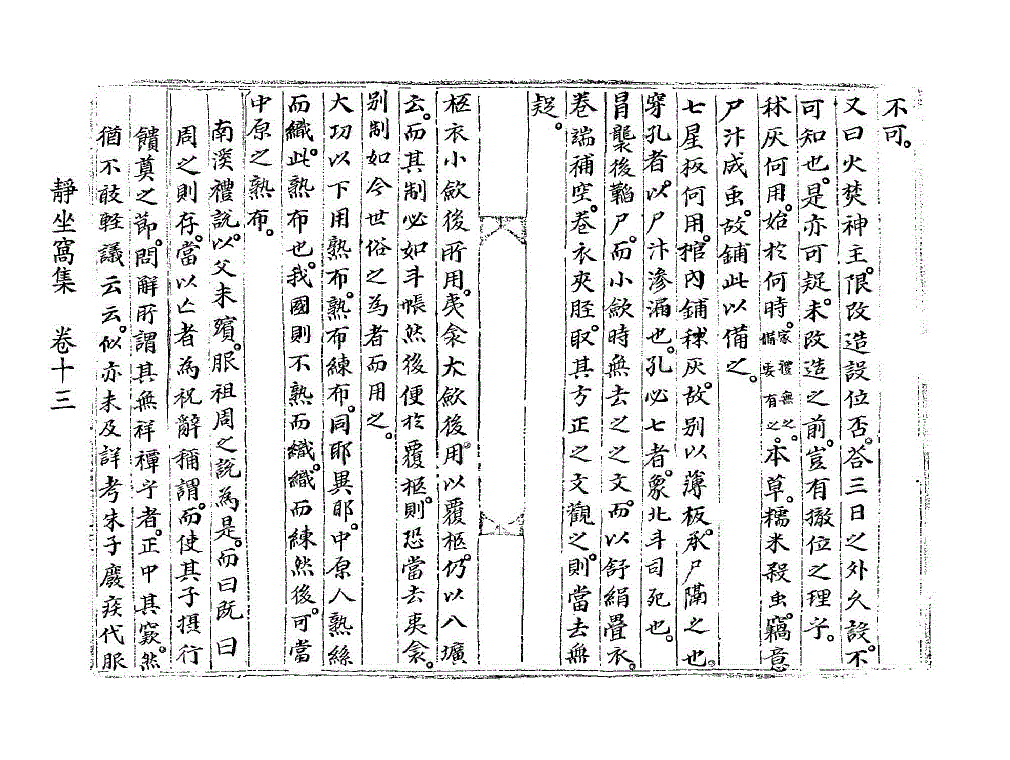 不可。
不可。又曰火焚神主。限改造设位否。答三日之外久设。不可知也。是亦可疑。未改造之前。岂有撤位之理乎。
秫灰何用。始于何时。(家礼无之。备要有之。)本草。糯米杀虫。窃意尸汁成虫。故铺此以备之。
七星板何用。棺内铺秫灰。故别以薄板。承尸隔之也。穿孔者。以尸汁渗漏也。孔必七者。象北斗司死也。
冒袭后韬尸。而小敛时无去之之文。而以舒绢叠衣。卷端补空。卷衣夹胫。取其方正之文观之。则当去无疑。
柩衣小敛后所用。夷衾大敛后。用以覆柩。仍以入圹云。而其制必如斗帐然后便于覆柩。则恐当去夷衾。别制如今世俗之为者而用之。
大功以下用熟布。熟布练布。同耶异耶。中原人熟丝而织。此熟布也。我国则不熟而织。织而练然后。可当中原之熟布。
南溪礼说。以父未殡。服祖周之说为是。而曰既曰周之则存。当以亡者为祝辞称谓。而使其子摄行馈奠之节。问解所谓其无祥禫乎者。正中其窾。然犹不敢轻议云云。似亦未及详考朱子废疾代服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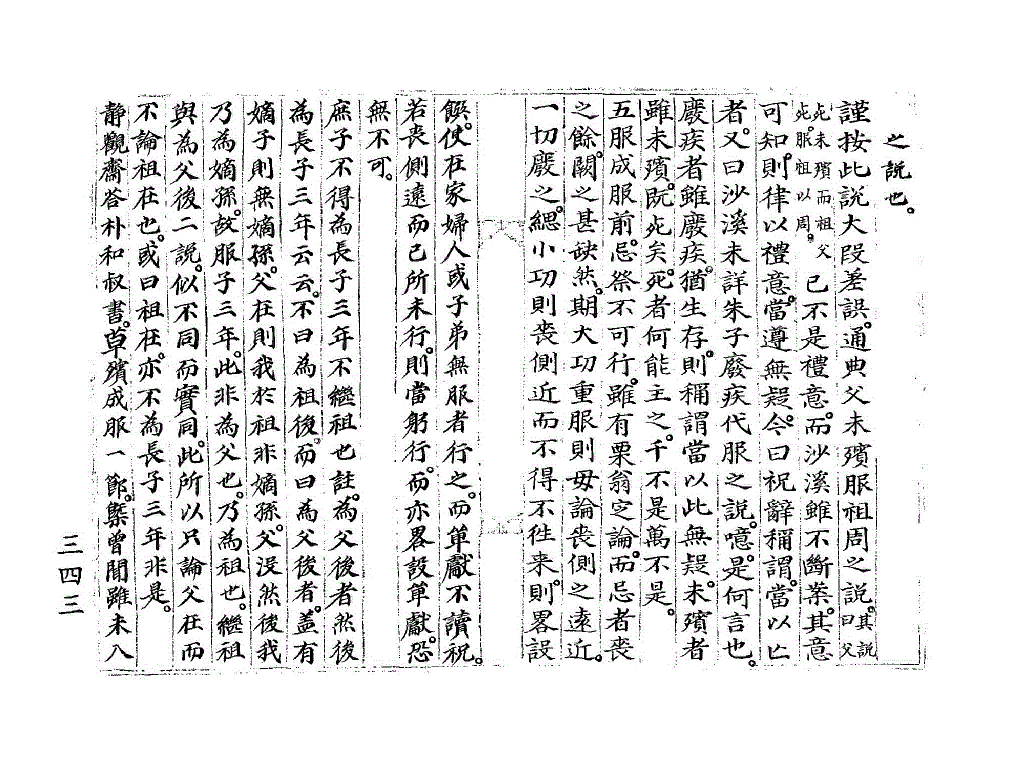 之说也。
之说也。谨按此说大段差误。通典父未殡服祖周之说。(其说曰父死未殡而祖父死。服祖以周。)已不是礼意。而沙溪虽不断案。其意可知。则律以礼意。当遵无疑。今曰祝辞称谓。当以亡者。又曰沙溪未详朱子废疾代服之说。噫。是何言也。废疾者虽废疾。犹生存。则称谓当以此无疑。未殡者虽未殡。既死矣。死者何能主之。千不是万不是。
五服成服前。忌祭不可行。虽有栗翁定论。而忌者丧之馀。阙之甚缺然。期大功重服则毋论丧侧之远近。一切废之。缌小功则丧侧近而不得不往来。则略设馔。使在家妇人或子弟无服者行之。而单献不读祝。若丧侧远而己所未行。则当躬行。而亦略设单献。恐无不可。
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注。为父后者然后为长子三年云云。不曰为祖后。而曰为父后者。盖有嫡子则无嫡孙。父在则我于祖非嫡孙。父没然后我乃为嫡孙。故服子三年。此非为父也。乃为祖也。继祖与为父后二说。似不同而实同。此所以只论父在而不论祖在也。或曰祖在。亦不为长子三年非是。
静观斋答朴和叔书。草殡成服一节。槩曾闻虽未入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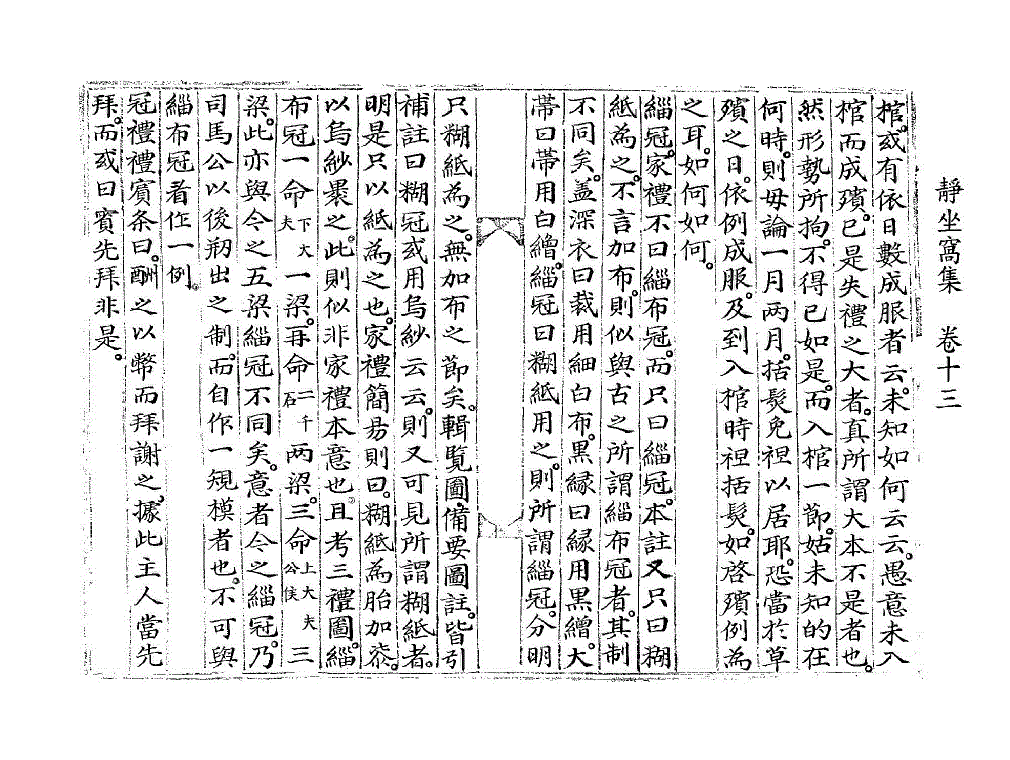 棺。或有依日数成服者云。未知如何云云。愚意未入棺而成殡。已是失礼之大者。真所谓大本不是者也。然形势所拘。不得已如是。而入棺一节。姑未知的在何时。则毋论一月两月。括发免袒以居耶。恐当于草殡之日。依例成服。及到入棺时袒括发。如启殡例为之耳。如何如何。
棺。或有依日数成服者云。未知如何云云。愚意未入棺而成殡。已是失礼之大者。真所谓大本不是者也。然形势所拘。不得已如是。而入棺一节。姑未知的在何时。则毋论一月两月。括发免袒以居耶。恐当于草殡之日。依例成服。及到入棺时袒括发。如启殡例为之耳。如何如何。缁冠。家礼不曰缁布冠。而只曰缁冠。本注又只曰糊纸为之。不言加布。则似与古之所谓缁布冠者。其制不同矣。盖深衣曰裁用细白布。黑缘曰缘用黑缯。大带曰带用白缯。缁冠曰糊纸用之。则所谓缁冠。分明只糊纸为之。无加布之节矣。辑览图,备要图注。皆引补注曰糊冠或用乌纱云云。则又可见所谓糊纸者。明是只以纸为之也。家礼简易则曰。糊纸为胎加漆。以乌纱裹之。此则似非家礼本意也。且考三礼图。缁布冠一命(下大夫)一梁。再命(二千石)两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三梁。此亦与今之五梁缁冠不同矣。意者今之缁冠。乃司马公以后刱出之制。而自作一规模者也。不可与缁布冠看作一例。
冠礼礼宾条曰。酬之以币而拜谢之。据此主人当先拜。而或曰宾先拜非是。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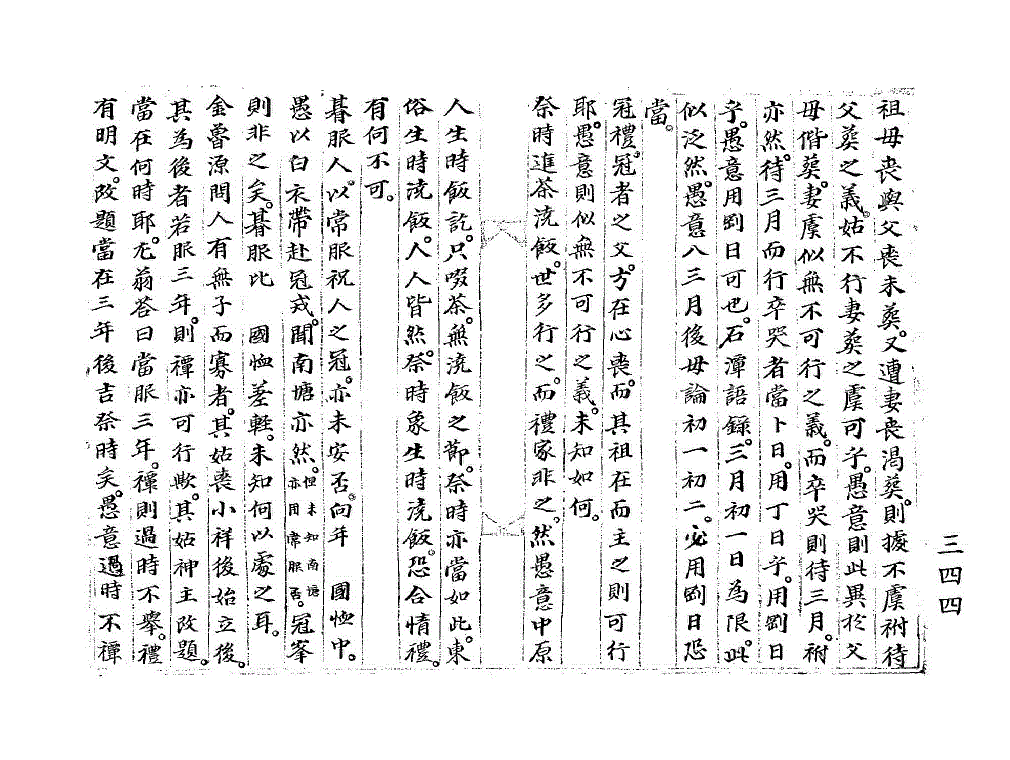 祖母丧与父丧未葬。又遭妻丧渴葬。则据不虞祔待父葬之义。姑不行妻葬之虞可乎。愚意则此异于父母偕葬。妻虞似无不可行之义。而卒哭则待三月。祔亦然。待三月而行卒哭者当卜日。用丁日乎。用刚日乎。愚意用刚日可也。石潭语录。三月初一日为限。此似泛然。愚意入三月后毋论初一初二。必用刚日恐当。
祖母丧与父丧未葬。又遭妻丧渴葬。则据不虞祔待父葬之义。姑不行妻葬之虞可乎。愚意则此异于父母偕葬。妻虞似无不可行之义。而卒哭则待三月。祔亦然。待三月而行卒哭者当卜日。用丁日乎。用刚日乎。愚意用刚日可也。石潭语录。三月初一日为限。此似泛然。愚意入三月后毋论初一初二。必用刚日恐当。冠礼。冠者之父。方在心丧。而其祖在而主之则可行耶。愚意则似无不可行之义。未知如何。
祭时进茶浇饭。世多行之。而礼家非之。然愚意中原人生时饭讫。只啜茶。无浇饭之节。祭时亦当如此。东俗生时浇饭。人人皆然。祭时象生时浇饭。恐合情礼。有何不可。
期服人。以常服祝人之冠。亦未安否。向年 国恤中。愚以白衣带赴冠戒。闻南塘亦然。(但未知南塘亦用常服否。)冠峰则非之矣。期服比 国恤差轻。未知何以处之耳。
金鲁源问人有无子而寡者。其姑丧小祥后始立后。其为后者若服三年。则禫亦可行欤。其姑神主改题。当在何时耶。尤翁答曰当服三年。禫则过时不举。礼有明文。改题当在三年后吉祭时矣。愚意过时不禫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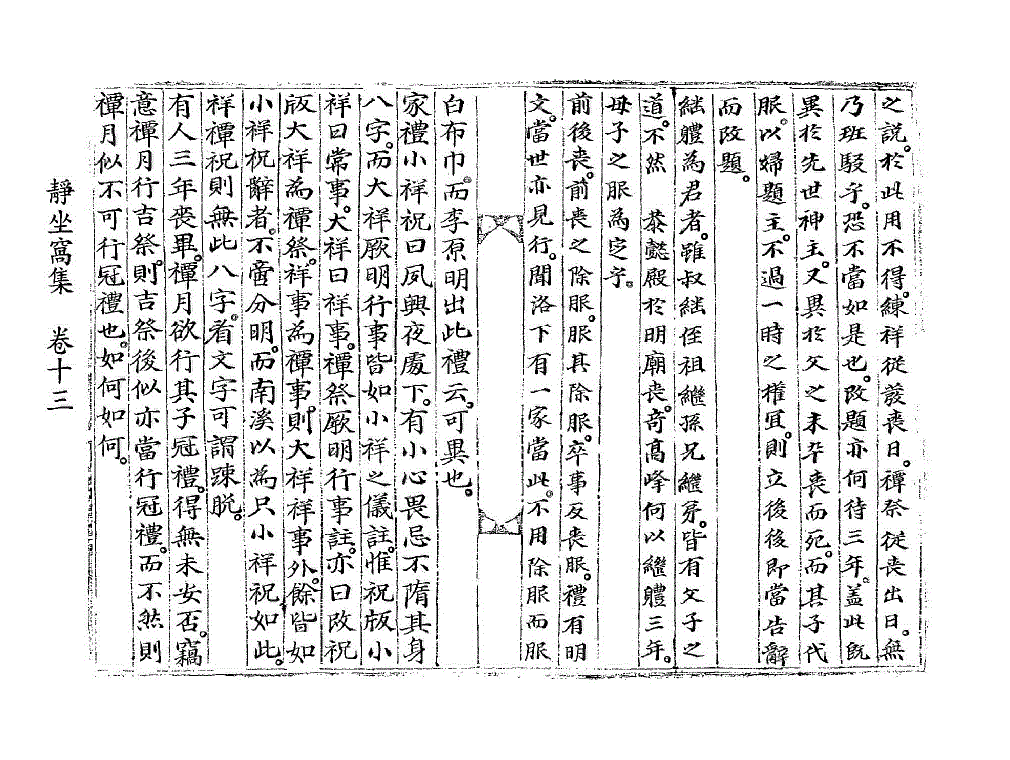 之说。于此用不得。练祥从发丧日。禫祭从丧出日。无乃班驳乎。恐不当如是也。改题亦何待三年。盖此既异于先世神主。又异于父之未卒丧而死。而其子代服。以妇题主。不过一时之权宜。则立后后即当告辞而改题。
之说。于此用不得。练祥从发丧日。禫祭从丧出日。无乃班驳乎。恐不当如是也。改题亦何待三年。盖此既异于先世神主。又异于父之未卒丧而死。而其子代服。以妇题主。不过一时之权宜。则立后后即当告辞而改题。继体为君者。虽叔继侄祖继孙兄继弟。皆有父子之道。不然 恭懿殿于明庙丧。奇高峰何以继体三年。母子之服为定乎。
前后丧。前丧之除服。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礼有明文。当世亦见行。闻洛下有一家当此。不用除服而服白布巾。而李原明出此礼云。可异也。
家礼小祥祝曰夙兴夜处下。有小心畏忌不隋其身八字。而大祥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仪注。惟祝版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禫祭厥明行事注。亦曰改祝版大祥为禫祭。祥事为禫事。则大祥祥事外。馀皆如小祥祝辞者。不啻分明。而南溪以为只小祥祝如此。祥禫祝则无此八字。看文字可谓疏脱。
有人三年丧毕。禫月欲行其子冠礼。得无未安否。窃意禫月行吉祭。则吉祭后似亦当行冠礼。而不然则禫月似不可行冠礼也。如何如何。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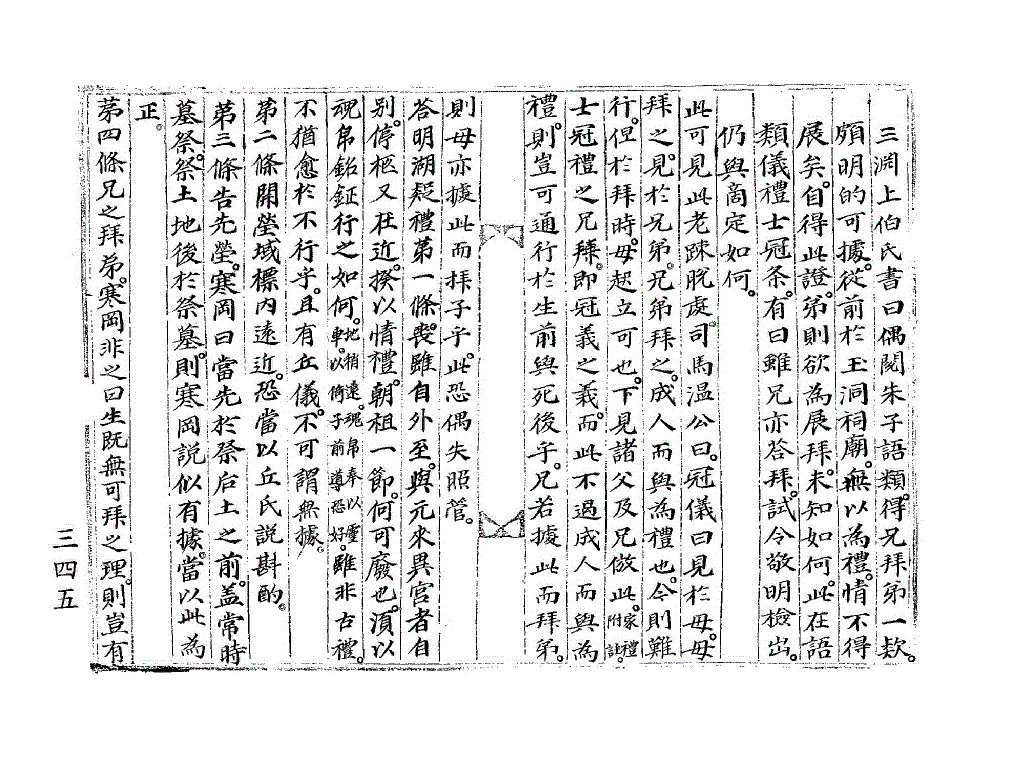 三渊上伯氏书曰偶阅朱子语类。得兄拜弟一款。颇明的可据。从前于玉洞祠庙。无以为礼。情不得展矣。自得此證。弟则欲为展拜。未知如何。此在语类仪礼士冠条。有曰虽兄亦答拜。试令敬明检出。乃与商定如何。
三渊上伯氏书曰偶阅朱子语类。得兄拜弟一款。颇明的可据。从前于玉洞祠庙。无以为礼。情不得展矣。自得此證。弟则欲为展拜。未知如何。此在语类仪礼士冠条。有曰虽兄亦答拜。试令敬明检出。乃与商定如何。此可见此老疏脱处。司马温公曰。冠仪曰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今则难行。但于拜时。母起立可也。下见诸父及兄仿此。(家礼附注。)士冠礼之兄拜。即冠义之义。而此不过成人而与为礼。则岂可通行于生前与死后乎。兄若据此而拜弟。则母亦据此而拜子乎。此恐偶失照管。
答明湖疑礼第一条。丧虽自外至。与元来异宫者自别。停柩又在近。揆以情礼。朝祖一节。何可废也。须以魂帛铭钲行之如何。(地稍远。魂帛奉以灵车。以倚子前导恐好。)虽非古礼。不犹愈于不行乎。且有丘仪。不可谓无据。
第二条开茔域标内远近。恐当以丘氏说斟酌。
第三条告先茔。寒冈曰当先于祭后土之前。盖常时墓祭。祭土地后于祭墓。则寒冈说似有据。当以此为正。
第四条兄之拜弟。寒冈非之曰生既无可拜之理。则岂有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6H 页
 遽变于既亡之后乎。其言甚是。尤翁于从弟。以不当拜言之。况于亲弟乎。但或人问祭子女弟侄。立耶坐耶。尤翁答曰丧礼尊长坐哭。祭礼亦岂异同。愚意祖于孙父于子叔于侄则坐哭。兄于弟则立哭。略示等杀恐当。未知如何。
遽变于既亡之后乎。其言甚是。尤翁于从弟。以不当拜言之。况于亲弟乎。但或人问祭子女弟侄。立耶坐耶。尤翁答曰丧礼尊长坐哭。祭礼亦岂异同。愚意祖于孙父于子叔于侄则坐哭。兄于弟则立哭。略示等杀恐当。未知如何。주-D003圣人之制丧服。其义不一。而条理间架。至为整齐。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缌。此一义也。服祖之子。同于祖。服曾祖之子。同于曾祖。服高祖之子。同于高祖。服兄弟之子。同于兄弟。此一义也。服父之子。不敢同于父。三年之丧。不可贰也。故降在期。
古礼嫡妇大功。故嫡孙妇为小功。后世加嫡妇期。而孙妇则不加矣。
三年之丧。不可二统。而自期以下。则无二统之嫌。降于父母。无二统也。不降于祖父母曾高祖。不敢薄于祖先也。降于兄弟侄。内夫家也。不降于其妻。不欲杀其兄弟侄之恩也。嫂叔无服。而娣姒妇相为服。意亦如此。嫂叔虽以远嫌而无服。娣姒相为服。即所以亲爱其兄弟如所谓。正伦理而笃恩义也。
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及兄弟之子。同在于期。而祖父母恩重义重而服轻。故不降。外亲比他功缌之亲。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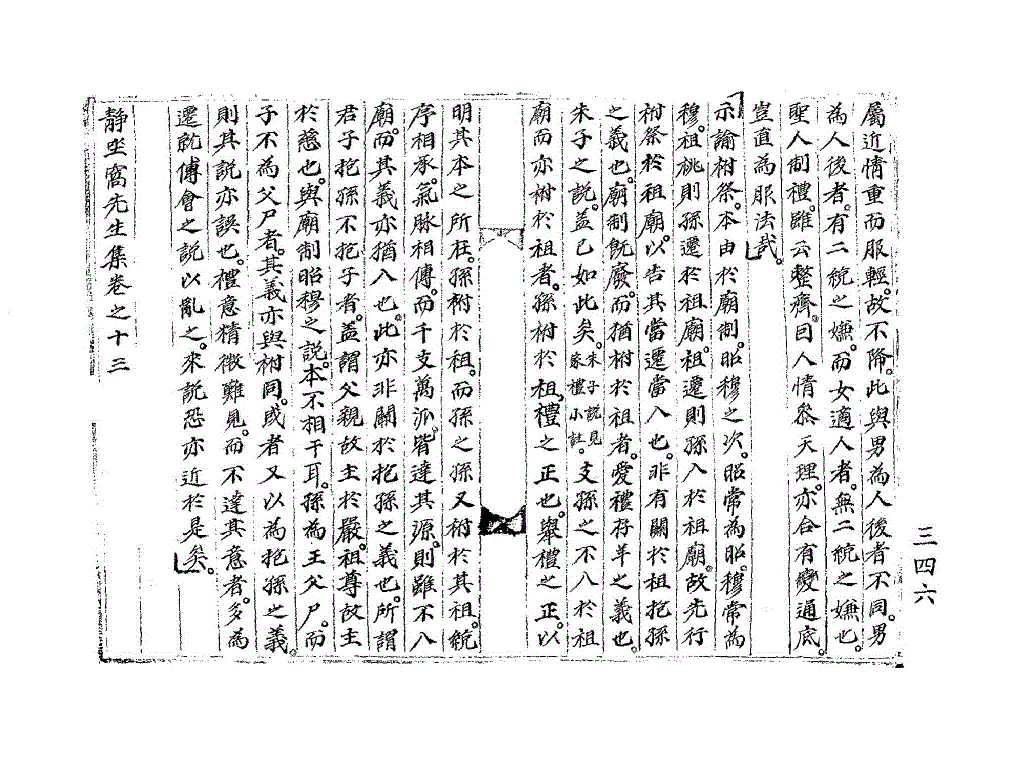 属近情重而服轻。故不降。此与男为人后者不同。男为人后者。有二统之嫌。而女适人者。无二统之嫌也。圣人制礼。虽云整齐。因人情参天理。亦合有变通底。岂直为服法哉。
属近情重而服轻。故不降。此与男为人后者不同。男为人后者。有二统之嫌。而女适人者。无二统之嫌也。圣人制礼。虽云整齐。因人情参天理。亦合有变通底。岂直为服法哉。示谕祔祭。本由于庙制。昭穆之次。昭常为昭。穆常为穆。祖祧则孙迁于祖庙。祖迁则孙入于祖庙。故先行祔祭于祖庙。以告其当迁当入也。非有关于祖抱孙之义也。庙制既废。而犹祔于祖者。爱礼存羊之义也。朱子之说。盖已如此矣。(朱子说见家礼小注。)支孙之不入于祖庙而亦祔于祖者。孙祔于祖。礼之正也。举礼之正。以明其本之所在。孙祔于祖。而孙之孙又祔于其祖。统序相承。气脉相传。而千支万派。皆达其源。则虽不入庙。而其义亦犹入也。此亦非关于抱孙之义也。所谓君子抱孙不抱子者。盖谓父亲故主于严。祖尊故主于慈也。与庙制昭穆之说。本不相干耳。孙为王父尸。而子不为父尸者。其义亦与祔同。或者又以为抱孙之义。则其说亦误也。礼意精微难见。而不达其意者。多为迁就傅会之说以乱之。来说恐亦近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