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x 页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书
书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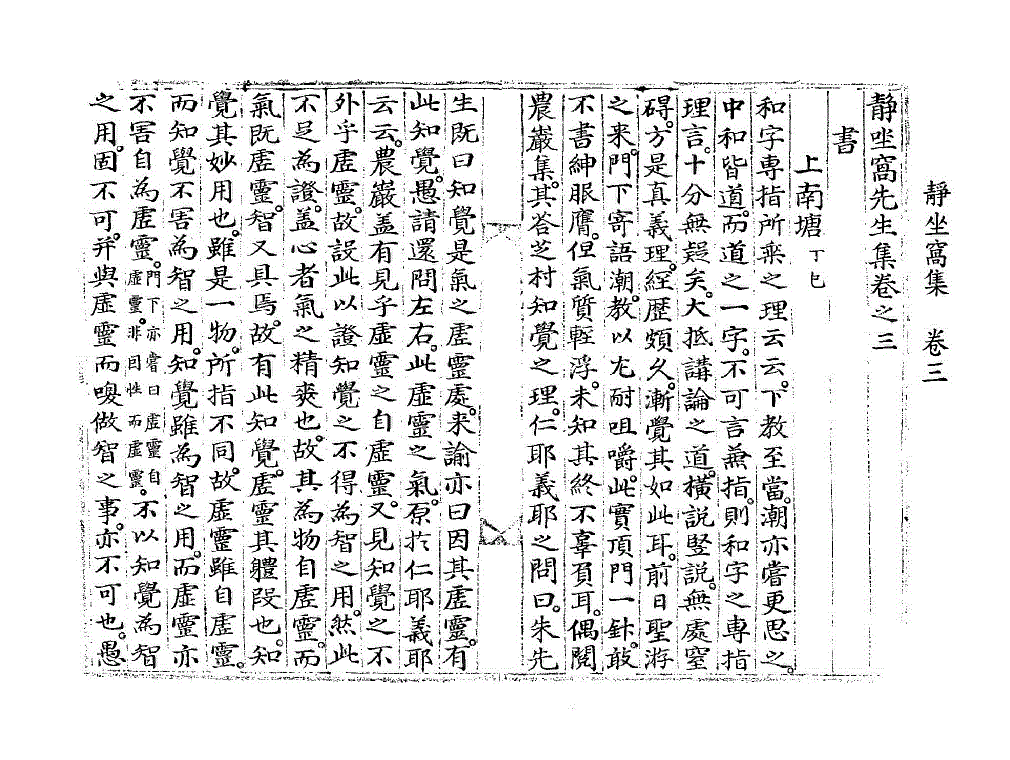 上南塘(丁巳)
上南塘(丁巳)和字专指所乘之理云云。下教至当。潮亦尝更思之。中和皆道。而道之一字。不可言兼指。则和字之专指理言。十分无疑矣。大抵讲论之道。横说竖说。无处窒碍。方是真义理。经历颇久。渐觉其如此耳。前日圣游之来。门下寄语潮。教以尤耐咀嚼。此实顶门一针。敢不书绅服膺。但气质轻浮。未知其终不辜负耳。偶阅农岩集。其答芝村知觉之理。仁耶义耶之问曰。朱先生既曰知觉是气之虚灵处。来谕亦曰因其虚灵。有此知觉。愚请还问左右。此虚灵之气。原于仁耶义耶云云。农岩盖有见乎虚灵之自虚灵。又见知觉之不外乎虚灵。故设此以證知觉之不得为智之用。然此不足为證。盖心者气之精爽也。故其为物自虚灵。而气既虚灵。智又具焉。故有此知觉。虚灵其体段也。知觉其妙用也。虽是一物。所指不同。故虚灵虽自虚灵。而知觉不害为智之用。知觉虽为智之用。而虚灵亦不害自为虚灵。(门下亦尝曰虚灵自虚灵。非因性而虚灵。)不以知觉为智之用。固不可。并与虚灵而唤做智之事。亦不可也。愚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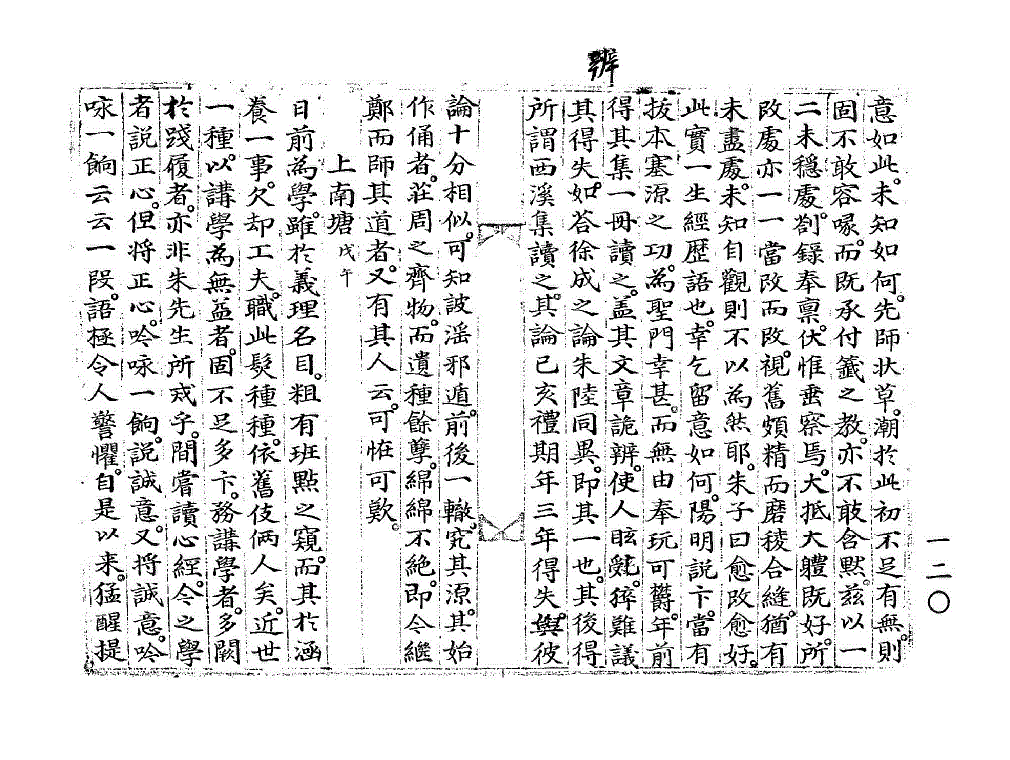 意如此。未知如何。先师状草。潮于此初不足有无。则固不敢容喙。而既承付签之教。亦不敢含默。玆以一二未稳处。劄录奉禀。伏惟垂察焉。大抵大体既好。所改处亦一一当改而改。视旧颇精而磨棱合缝。犹有未尽处。未知自观则不以为然耶。朱子曰愈改愈好。此实一生经历语也。幸乞留意如何。阳明说卞。当有拔本塞源之功。为圣门幸甚。而无由奉玩可郁。年前得其集一册读之。盖其文章诡辨(一作辩)。使人眩乱。猝难议其得失。如答徐成之论朱陆同异。即其一也。其后得所谓西溪集读之。其论己亥礼期年三年得失。与彼论十分相似。可知诐淫邪遁。前后一辙。究其源。其始作俑者。庄周之齐物。而遗种馀孽。绵绵不绝。即今继郑而师其道者。又有其人云。可怪可叹。
意如此。未知如何。先师状草。潮于此初不足有无。则固不敢容喙。而既承付签之教。亦不敢含默。玆以一二未稳处。劄录奉禀。伏惟垂察焉。大抵大体既好。所改处亦一一当改而改。视旧颇精而磨棱合缝。犹有未尽处。未知自观则不以为然耶。朱子曰愈改愈好。此实一生经历语也。幸乞留意如何。阳明说卞。当有拔本塞源之功。为圣门幸甚。而无由奉玩可郁。年前得其集一册读之。盖其文章诡辨(一作辩)。使人眩乱。猝难议其得失。如答徐成之论朱陆同异。即其一也。其后得所谓西溪集读之。其论己亥礼期年三年得失。与彼论十分相似。可知诐淫邪遁。前后一辙。究其源。其始作俑者。庄周之齐物。而遗种馀孽。绵绵不绝。即今继郑而师其道者。又有其人云。可怪可叹。上南塘(戊午)
日前为学。虽于义理名目。粗有班点之窥。而其于涵养一事。欠却工夫。职此发种种。依旧伎俩人矣。近世一种。以讲学为无益者。固不足多卞。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者。亦非朱先生所戒乎。间尝读心经。今之学者说正心。但将正心。吟咏一饷。说诚意。又将诚意。吟咏一饷云云一段。语极令人警惧。自是以来。猛醒提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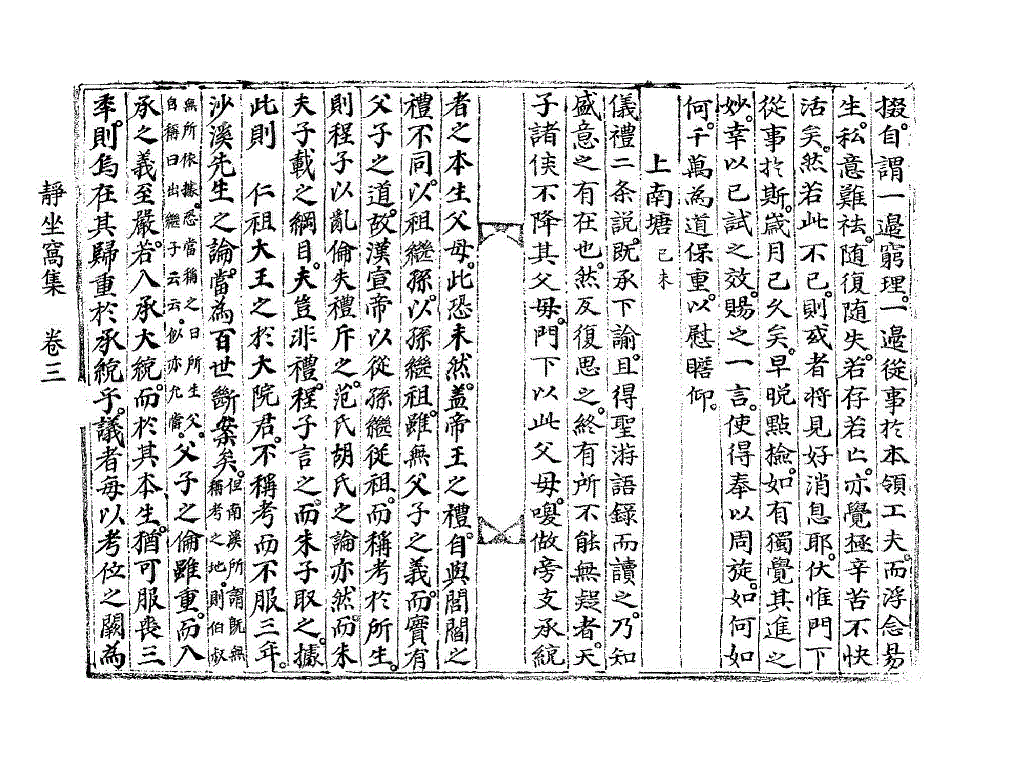 掇。自谓一边穷理。一边从事于本领工夫。而浮念易生。私意难祛。随复随失。若存若亡。亦觉极辛苦不快活矣。然若此不已。则或者将见好消息耶。伏惟门下从事于斯。岁月已久矣。早晚点检。如有独觉其进之妙。幸以已试之效。赐之一言。使得奉以周旋。如何如何。千万为道保重。以慰瞻仰。
掇。自谓一边穷理。一边从事于本领工夫。而浮念易生。私意难祛。随复随失。若存若亡。亦觉极辛苦不快活矣。然若此不已。则或者将见好消息耶。伏惟门下从事于斯。岁月已久矣。早晚点检。如有独觉其进之妙。幸以已试之效。赐之一言。使得奉以周旋。如何如何。千万为道保重。以慰瞻仰。上南塘(己未)
仪礼二条说。既承下谕。且得圣游语录而读之。乃知盛意之有在也。然反复思之。终有所不能无疑者。天子诸侯不降其父母。门下以此父母。唤做旁支承统者之本生父母。此恐未然。盖帝王之礼。自与闾阎之礼不同。以祖继孙。以孙继祖。虽无父子之义。而实有父子之道。故汉宣帝以从孙继从祖。而称考于所生。则程子以乱伦失礼斥之。范氏胡氏之论亦然。而朱夫子载之纲目。夫岂非礼。程子言之。而朱子取之。据此则 仁祖大王之于大院君。不称考而不服三年。沙溪先生之论。当为百世断案矣。(但南溪所谓既无称考之地。则伯叔无所依据。恐当称之曰所生父。自称曰出继子云云。似亦允当。)父子之伦虽重。而入承之义至严。若入承大统。而于其本生。犹可服丧三年。则乌在其归重于承统乎。议者每以考位之阙为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1L 页
 言。此皆以士庶人之礼论之。而殊不知帝王家礼自当别论也。入承者之于先王。虽非父子。而继世一事。无异父子。故先王为昭。则入承者无论祖孙叔侄。自当为穆。先王为穆。则入承者亦无论祖孙叔侄。自当为昭。昭穆非父子之道乎。昭穆既定于王家。而犹以考位之阙。乃反称考于本生而服丧。则岂非所谓半上落下者乎。且以臣为君之父母。为旁支君之本生父母。而又谓看作创业之君。则天子不与焉。亦恐未安。天子之父。生而虽为太上。既无食之之恩。则臣民岂有服三年之义乎。创业之君。既为天子矣。太上又为天子。而于其死也。亦服三年。则是二天子矣。其可乎。愚意无论天子诸侯。创业之君。则臣民为其父母。皆当服期。未知如何。正统之期一款。更考仪礼正统旁期啚。上则曰祖父母期。下则曰孙曾玄嫡则皆期。据此则正统之期。非但祖父母。嫡孙曾玄皆包在其中。(祖父母期。惟创业之君为然。嫡孙曾玄之期。则非但创业之君。承继之君亦然。)此则按啚可见。不须致疑。至于嫡子。则啚式曰长子斩衰。(此亦正统旁期啚。)来谕不降条参看云云。恐失照勘。更考之如何。鬼神说两度书。皆得而读之。考据该博。议论精密。诚可谓断案。愚何敢间然乎。静默二字。谨当服膺。而时
言。此皆以士庶人之礼论之。而殊不知帝王家礼自当别论也。入承者之于先王。虽非父子。而继世一事。无异父子。故先王为昭。则入承者无论祖孙叔侄。自当为穆。先王为穆。则入承者亦无论祖孙叔侄。自当为昭。昭穆非父子之道乎。昭穆既定于王家。而犹以考位之阙。乃反称考于本生而服丧。则岂非所谓半上落下者乎。且以臣为君之父母。为旁支君之本生父母。而又谓看作创业之君。则天子不与焉。亦恐未安。天子之父。生而虽为太上。既无食之之恩。则臣民岂有服三年之义乎。创业之君。既为天子矣。太上又为天子。而于其死也。亦服三年。则是二天子矣。其可乎。愚意无论天子诸侯。创业之君。则臣民为其父母。皆当服期。未知如何。正统之期一款。更考仪礼正统旁期啚。上则曰祖父母期。下则曰孙曾玄嫡则皆期。据此则正统之期。非但祖父母。嫡孙曾玄皆包在其中。(祖父母期。惟创业之君为然。嫡孙曾玄之期。则非但创业之君。承继之君亦然。)此则按啚可见。不须致疑。至于嫡子。则啚式曰长子斩衰。(此亦正统旁期啚。)来谕不降条参看云云。恐失照勘。更考之如何。鬼神说两度书。皆得而读之。考据该博。议论精密。诚可谓断案。愚何敢间然乎。静默二字。谨当服膺。而时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2H 页
 有不得不开口处。近又与寒泉论斥心纯善之说。而及见回报。落落难合。初不如静默之为愈也。盖其主意以心为纯善。乃以本体之湛一者当之。而谓于未发前见之。以本禀清浊。归之于已发之后。而曰未发不可着气质字。难之者曰心气也。气既不齐。则心岂纯善乎。则曰自古论心。未有单言气者。必合性言之。其义乃备。隐然以合性为纯善之證。且曰专以气言心。则是主张气字太过。近于善恶混之说。岂不疏谬可笑乎。愚将欲以一转语答之曰只言虚灵则虽不兼言性。不害圣凡之皆同。统言心则虽兼言性。难掩清浊之不齐。未知如何。
有不得不开口处。近又与寒泉论斥心纯善之说。而及见回报。落落难合。初不如静默之为愈也。盖其主意以心为纯善。乃以本体之湛一者当之。而谓于未发前见之。以本禀清浊。归之于已发之后。而曰未发不可着气质字。难之者曰心气也。气既不齐。则心岂纯善乎。则曰自古论心。未有单言气者。必合性言之。其义乃备。隐然以合性为纯善之證。且曰专以气言心。则是主张气字太过。近于善恶混之说。岂不疏谬可笑乎。愚将欲以一转语答之曰只言虚灵则虽不兼言性。不害圣凡之皆同。统言心则虽兼言性。难掩清浊之不齐。未知如何。上南塘别纸
圣游人心之中节者。即是道心云云。门下非之是矣。然考诸栗谷文字。则人心道心说曰人心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亦为道心矣。答牛溪书曰马㥧人心。不待牵制而自由正路。则圣人之从心所欲。而人心亦道心者。 经筵日记。告君曰人心中节。则人心亦道心矣。据此则圣游之言。亦有所据矣。然虽是栗谷为之言。不能无疑。人心之中节者。即是道心。而在圣人分上。浑是道心。则中庸序文。何以曰上智不能无人心乎。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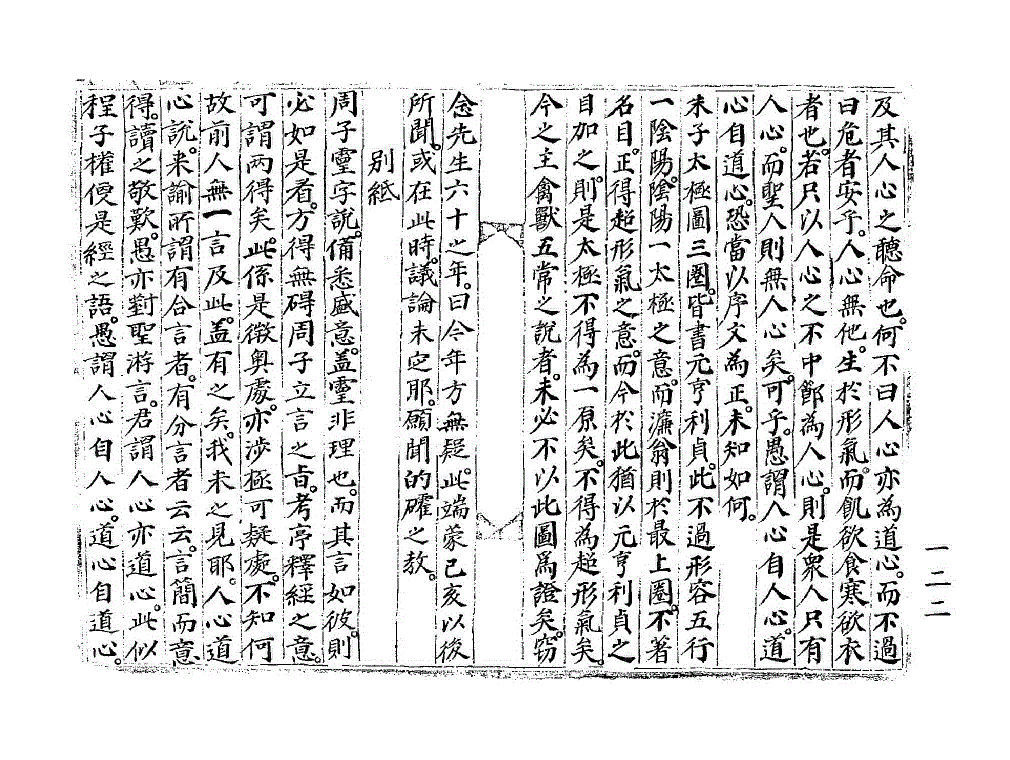 及其人心之听命也。何不曰人心亦为道心。而不过曰危者安乎。人心无他。生于形气。而饥欲食寒欲衣者也。若只以人心之不中节为人心。则是众人只有人心。而圣人则无人心矣。可乎。愚谓人心自人心。道心自道心。恐当以序文为正。未知如何。
及其人心之听命也。何不曰人心亦为道心。而不过曰危者安乎。人心无他。生于形气。而饥欲食寒欲衣者也。若只以人心之不中节为人心。则是众人只有人心。而圣人则无人心矣。可乎。愚谓人心自人心。道心自道心。恐当以序文为正。未知如何。朱子太极图三圈。皆书元亨利贞。此不过形容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之意。而濂翁则于最上圈。不著名目。正得超形气之意。而今于此犹以元亨利贞之目加之。则是太极不得为一原矣。不得为超形气矣。今之主禽兽五常之说者。未必不以此图为證矣。窃念先生六十之年。曰今年方无疑。此端蒙己亥以后所闻。或在此时。议论未定耶。愿闻的礭之教。
别纸
周子灵字说。备悉盛意。盖灵非理也。而其言如彼。则必如是看。方得无碍周子立言之旨。考亭释经之意。可谓两得矣。此系是微奥处。亦涉极可疑处。不知何故前人无一言及此。盖有之矣。我未之见耶。人心道心说。来谕所谓有合言者。有分言者云云。言简而意得。读之敬叹。愚亦对圣游言。君谓人心亦道心。此似程子权便是经之语。愚谓人心自人心。道心自道心。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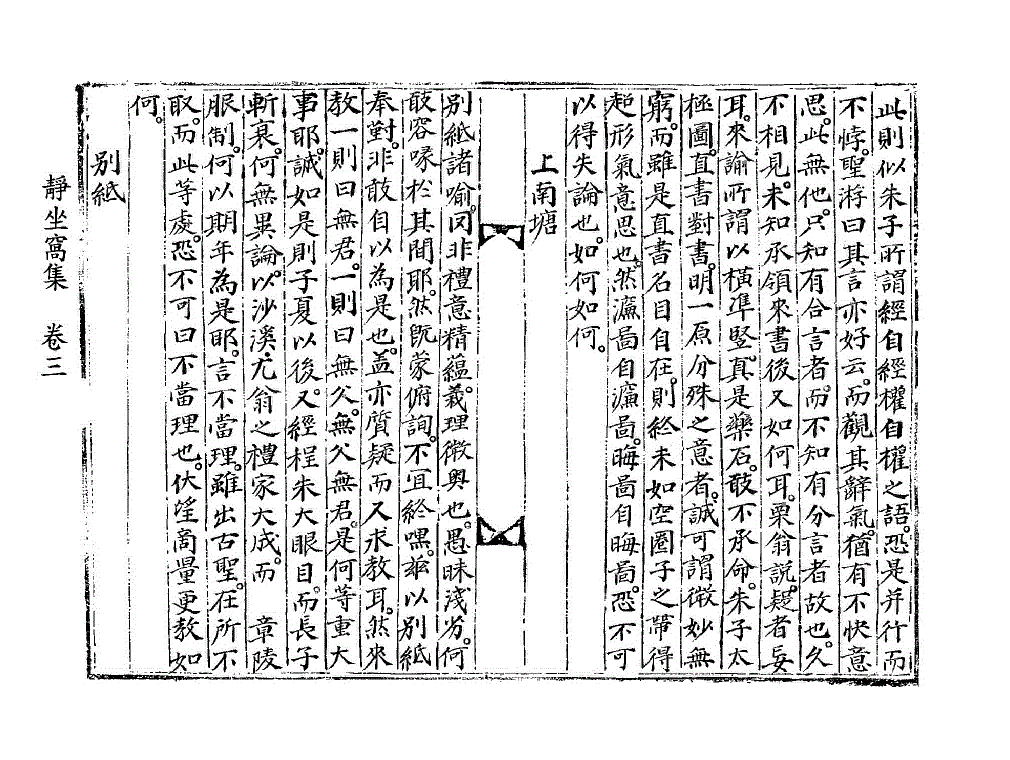 此则似朱子所谓经自经权自权之语。恐是并行而不悖。圣游曰其言亦好云。而观其辞气。犹有不快意思。此无他。只知有合言者。而不知有分言者故也。久不相见。未知承领来书后又如何耳。栗翁说。疑者妄耳。来谕所谓以横准竖。真是药石。敢不承命。朱子太极图。直书对书。明一原分殊之意者。诚可谓微妙无穷。而虽是直书名目自在。则终未如空圈子之带得超形气意思也。然濂啚自濂啚。晦啚自晦啚。恐不可以得失论也。如何如何。
此则似朱子所谓经自经权自权之语。恐是并行而不悖。圣游曰其言亦好云。而观其辞气。犹有不快意思。此无他。只知有合言者。而不知有分言者故也。久不相见。未知承领来书后又如何耳。栗翁说。疑者妄耳。来谕所谓以横准竖。真是药石。敢不承命。朱子太极图。直书对书。明一原分殊之意者。诚可谓微妙无穷。而虽是直书名目自在。则终未如空圈子之带得超形气意思也。然濂啚自濂啚。晦啚自晦啚。恐不可以得失论也。如何如何。上南塘
别纸诸喻。罔非礼意精蕴。义理微奥也。愚昧浅劣。何敢容喙于其间耶。然既蒙俯询。不宜终嘿。玆以别纸奉对。非敢自以为是也。盖亦质疑而又求教耳。然来教一则曰无君。一则曰无父。无父无君。是何等重大事耶。诚如是则子夏以后。又经程朱大眼目。而长子斩衰。何无异论。以沙溪,尤翁之礼家大成。而 章陵服制。何以期年为是耶。言不当理。虽出古圣。在所不取。而此等处。恐不可曰不当理也。伏望商量更教如何。
别纸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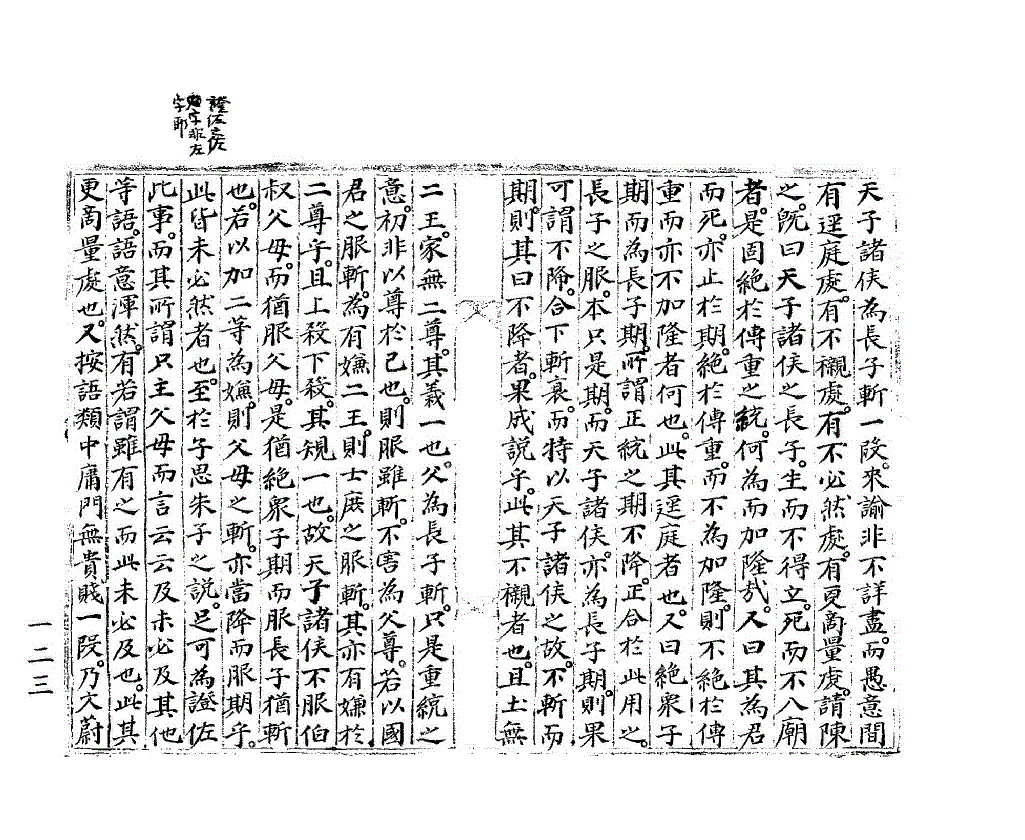 天子诸侯为长子斩一段。来谕非不详尽。而愚意间有径庭处。有不衬处。有不必然处。有更商量处。请陈之。既曰天子诸侯之长子。生而不得立。死而不入庙者。是固绝于传重之统。何为而加隆哉。又曰其为君而死。亦止于期。绝于传重。而不为加隆。则不绝于传重而亦不加隆者何也。此其径庭者也。又曰绝众子期而为长子期。所谓正统之期不降。正合于此用之。长子之服。本只是期。而天子诸侯。亦为长子期。则果可谓不降。合下斩衰。而特以天子诸侯之故。不斩而期。则其曰不降者。果成说乎。此其不衬者也。且土无二王。家无二尊。其义一也父为长子斩。只是重统之意。初非以尊于己也。则服虽斩。不害为父尊。若以国君之服斩。为有嫌二王。则士庶之服斩。其亦有嫌于二尊乎。且上杀下杀。其规一也。故天子诸侯不服伯叔父母。而犹服父母。是犹绝众子期而服长子犹斩也。若以加二等为嫌。则父母之斩。亦当降而服期乎。此皆未必然者也。至于子思朱子之说。足可为證佐(證佐之佐字。非左字耶。)此事。而其所谓只主父母而言云云及未必及其他等语。语意浑然。有若谓虽有之而此未必及也。此其更商量处也。又按语类中庸门无贵贱一段。乃文蔚
天子诸侯为长子斩一段。来谕非不详尽。而愚意间有径庭处。有不衬处。有不必然处。有更商量处。请陈之。既曰天子诸侯之长子。生而不得立。死而不入庙者。是固绝于传重之统。何为而加隆哉。又曰其为君而死。亦止于期。绝于传重。而不为加隆。则不绝于传重而亦不加隆者何也。此其径庭者也。又曰绝众子期而为长子期。所谓正统之期不降。正合于此用之。长子之服。本只是期。而天子诸侯。亦为长子期。则果可谓不降。合下斩衰。而特以天子诸侯之故。不斩而期。则其曰不降者。果成说乎。此其不衬者也。且土无二王。家无二尊。其义一也父为长子斩。只是重统之意。初非以尊于己也。则服虽斩。不害为父尊。若以国君之服斩。为有嫌二王。则士庶之服斩。其亦有嫌于二尊乎。且上杀下杀。其规一也。故天子诸侯不服伯叔父母。而犹服父母。是犹绝众子期而服长子犹斩也。若以加二等为嫌。则父母之斩。亦当降而服期乎。此皆未必然者也。至于子思朱子之说。足可为證佐(證佐之佐字。非左字耶。)此事。而其所谓只主父母而言云云及未必及其他等语。语意浑然。有若谓虽有之而此未必及也。此其更商量处也。又按语类中庸门无贵贱一段。乃文蔚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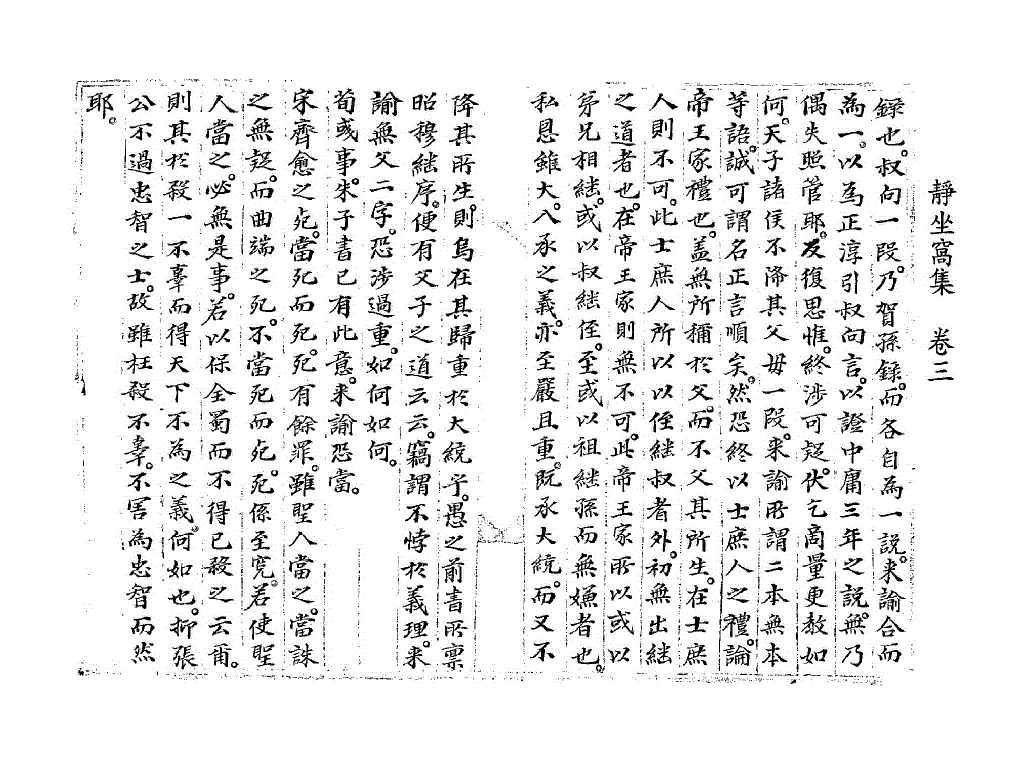 录也。叔向一段。乃贺孙录。而各自为一说。来谕合而为一。以为正淳引叔向言。以證中庸三年之说。无乃偶失照管耶。反复思惟。终涉可疑。伏乞商量更教如何。天子诸侯不降其父母一段。来谕所谓二本无本等语。诚可谓名正言顺矣。然恐终以士庶人之礼。论帝王家礼也。盖无所称于父。而不父其所生。在士庶人则不可。此士庶人所以以侄继叔者外。初无出继之道者也。在帝王家则无不可。此帝王家所以或以弟兄相继。或以叔继侄。至或以祖继孙而无嫌者也。私恩虽大。入承之义。亦至严且重。既承大统。而又不降其所生。则乌在其归重于大统乎。愚之前书所禀昭穆继序。便有父子之道云云。窃谓不悖于义理。来谕无父二字。恐涉过重。如何如何。
录也。叔向一段。乃贺孙录。而各自为一说。来谕合而为一。以为正淳引叔向言。以證中庸三年之说。无乃偶失照管耶。反复思惟。终涉可疑。伏乞商量更教如何。天子诸侯不降其父母一段。来谕所谓二本无本等语。诚可谓名正言顺矣。然恐终以士庶人之礼。论帝王家礼也。盖无所称于父。而不父其所生。在士庶人则不可。此士庶人所以以侄继叔者外。初无出继之道者也。在帝王家则无不可。此帝王家所以或以弟兄相继。或以叔继侄。至或以祖继孙而无嫌者也。私恩虽大。入承之义。亦至严且重。既承大统。而又不降其所生。则乌在其归重于大统乎。愚之前书所禀昭穆继序。便有父子之道云云。窃谓不悖于义理。来谕无父二字。恐涉过重。如何如何。荀彧事。朱子书已有此意。来谕恐当。
宋齐愈之死。当死而死。死有馀罪。虽圣人当之。当诛之无疑。而曲端之死。不当死而死。死系至冤。若使圣人当之。必无是事。若以保全蜀而不得已杀之云尔。则其于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义。何如也。抑张公不过忠智之士。故虽枉杀不辜。不害为忠智而然耶。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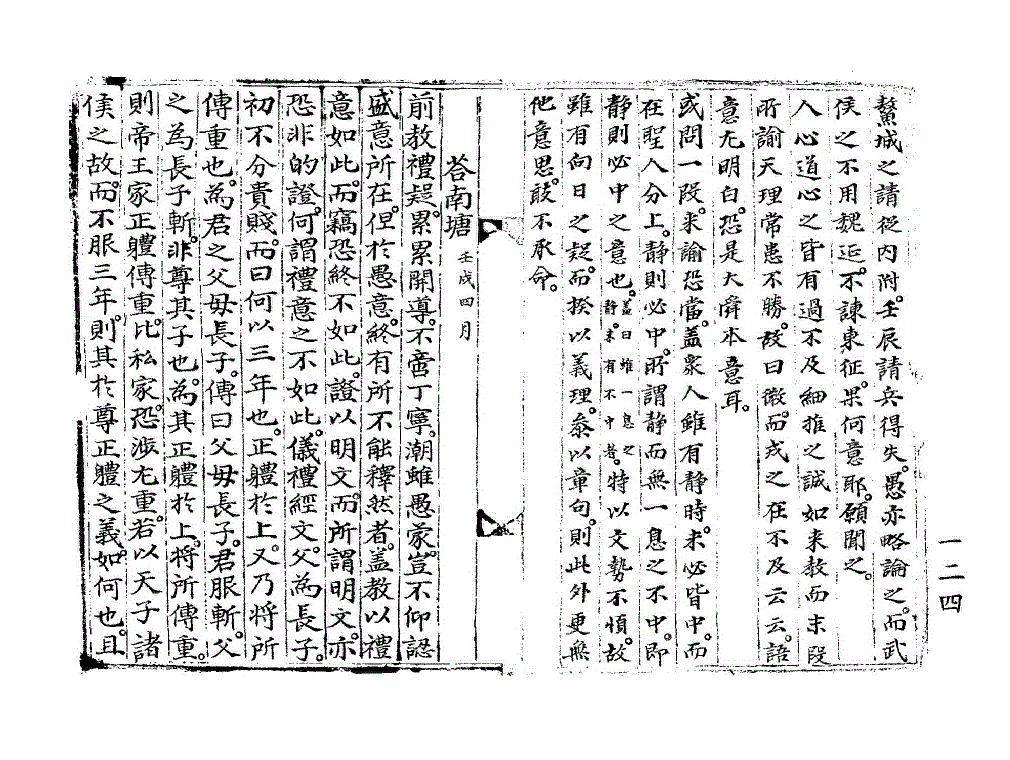 鳌城之请从内附。壬辰请兵得失。愚亦略论之。而武侯之不用魏延。不谏东征。果何意耶。愿闻之。
鳌城之请从内附。壬辰请兵得失。愚亦略论之。而武侯之不用魏延。不谏东征。果何意耶。愿闻之。人心道心之皆有过不及细推之诚如来教而末段所谕天理常患不胜。故曰微。而戒之在不及云云。语意尤明白。恐是大舜本意耳。
或问一段。来谕恐当。盖众人虽有静时。未必皆中。而在圣人分上。静则必中。所谓静而无一息之不中。即静则必中之意也。(盖曰虽一息之静。未有不中者。)特以文势不㥧。故虽有向日之疑。而揆以义理。参以章句。则此外更无他意思。敢不承命。
答南塘(壬戌四月)
前教礼疑。累累开导。不啻丁宁。潮虽愚蒙。岂不仰认盛意所在。但于愚意。终有所不能释然者。盖教以礼意如此。而窃恐终不如此。證以明文。而所谓明文。亦恐非的證。何谓礼意之不如此。仪礼经文。父为长子。初不分贵贱。而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为君之父母长子。传曰父母长子。君服斩。父之为长子斩。非尊其子也。为其正体于上。将所传重。则帝王家正体传重。比私家。恐涉尤重。若以天子诸侯之故。而不服三年。则其于尊正体之义。如何也。且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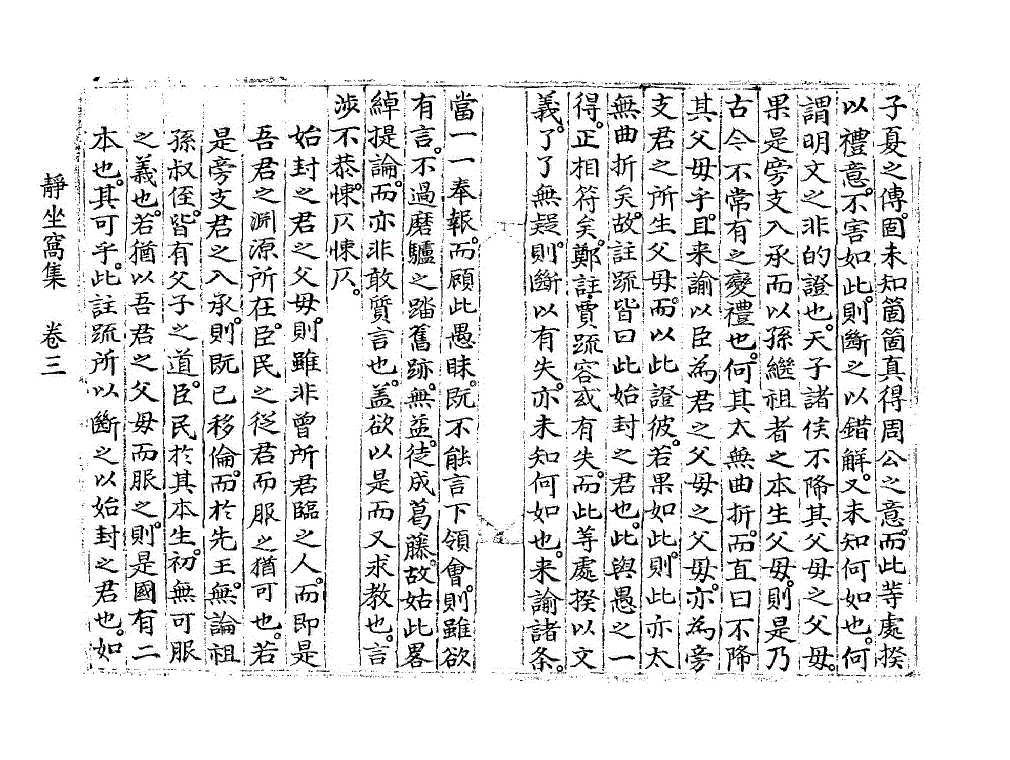 子夏之传。固未知个个真得周公之意。而此等处揆以礼意。不害如此。则断之以错解。又未知何如也。何谓明文之非的證也。天子诸侯不降其父母之父母。果是旁支入承而以孙继祖者之本生父母。则是乃古今不常有之变礼也。何其太无曲折。而直曰不降其父母乎。且来谕以臣为君之父母之父母。亦为旁支君之所生父母。而以此證彼。若果如此。则此亦太无曲折矣。故注疏皆曰此始封之君也。此与愚之一得。正相符矣。郑注,贾疏容或有失。而此等处揆以文义。了了无疑。则断以有失。亦未知何如也。来谕诸条。当一一奉报。而顾此愚昧。既不能言下领会。则虽欲有言。不过磨驴之踏旧迹。无益。徒成葛藤。故姑此略绰提论。而亦非敢质言也。盖欲以是而又求教也。言涉不恭。悚仄悚仄。
子夏之传。固未知个个真得周公之意。而此等处揆以礼意。不害如此。则断之以错解。又未知何如也。何谓明文之非的證也。天子诸侯不降其父母之父母。果是旁支入承而以孙继祖者之本生父母。则是乃古今不常有之变礼也。何其太无曲折。而直曰不降其父母乎。且来谕以臣为君之父母之父母。亦为旁支君之所生父母。而以此證彼。若果如此。则此亦太无曲折矣。故注疏皆曰此始封之君也。此与愚之一得。正相符矣。郑注,贾疏容或有失。而此等处揆以文义。了了无疑。则断以有失。亦未知何如也。来谕诸条。当一一奉报。而顾此愚昧。既不能言下领会。则虽欲有言。不过磨驴之踏旧迹。无益。徒成葛藤。故姑此略绰提论。而亦非敢质言也。盖欲以是而又求教也。言涉不恭。悚仄悚仄。始封之君之父母。则虽非曾所君临之人。而即是吾君之渊源所在。臣民之从君而服之犹可也。若是旁支君之入承。则既已移伦。而于先王。无论祖孙叔侄。皆有父子之道。臣民于其本生。初无可服之义也。若犹以吾君之父母而服之。则是国有二本也。其可乎。此注疏所以断之以始封之君也。如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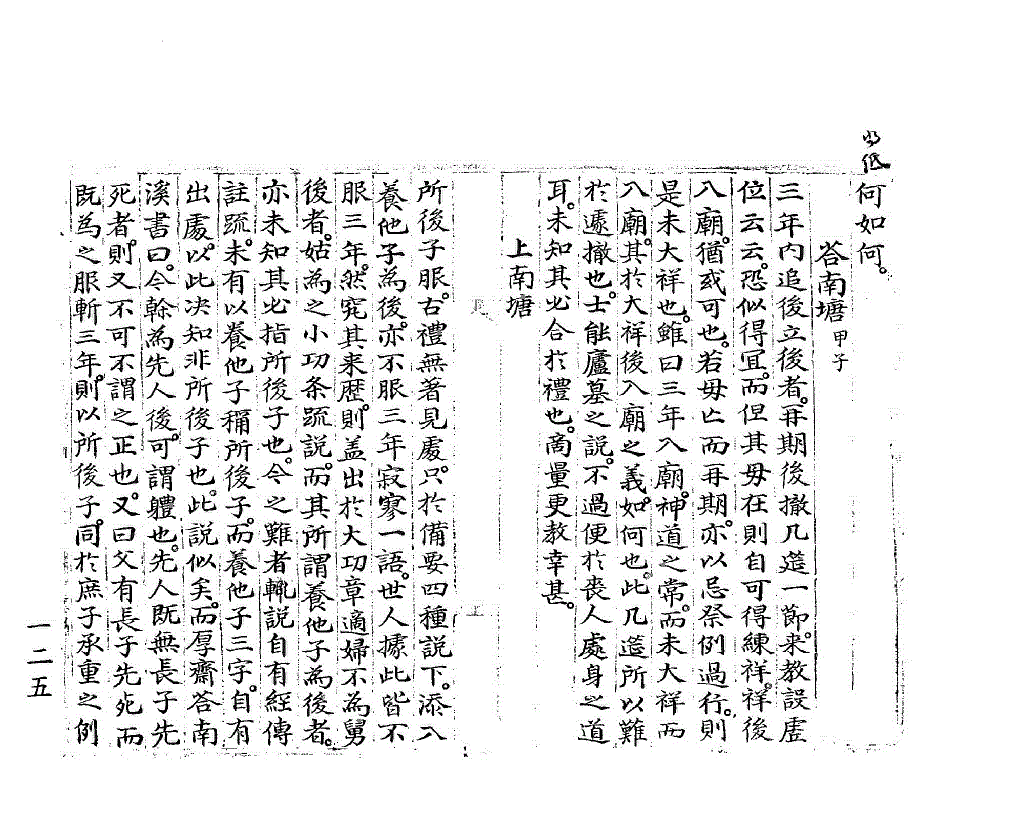 주-D001何如何。
주-D001何如何。答南塘(甲子)
三年内追后立后者。再期后撤几筵一节。来教设虚位云云。恐似得宜。而但其母在则自可得练祥。祥后入庙。犹或可也。若母亡而再期。亦以忌祭例过行。则是未大祥也。虽曰三年入庙。神道之常。而未大祥而入庙。其于大祥后入庙之义。如何也。此几筵所以难于遽撤也。士能庐墓之说。不过便于丧人处身之道耳。未知其必合于礼也。商量更教幸甚。
上南塘
所后子服。古礼无著见处。只于备要四种说下。添入养他子为后。亦不服三年寂寥一语。世人据此皆不服三年。然究其来历。则盖出于大功章适妇不为舅后者。姑为之小功条疏说。而其所谓养他子为后者。亦未知其必指所后子也。今之难者辄说自有经传注疏。未有以养他子称所后子。而养他子三字。自有出处。以此决知非所后子也。此说似矣。而厚斋答南溪书曰。今干为先人后。可谓体也。先人既无长子先死者。则又不可不谓之正也。又曰父有长子先死而既为之服斩三年。则以所后子。同于庶子承重之例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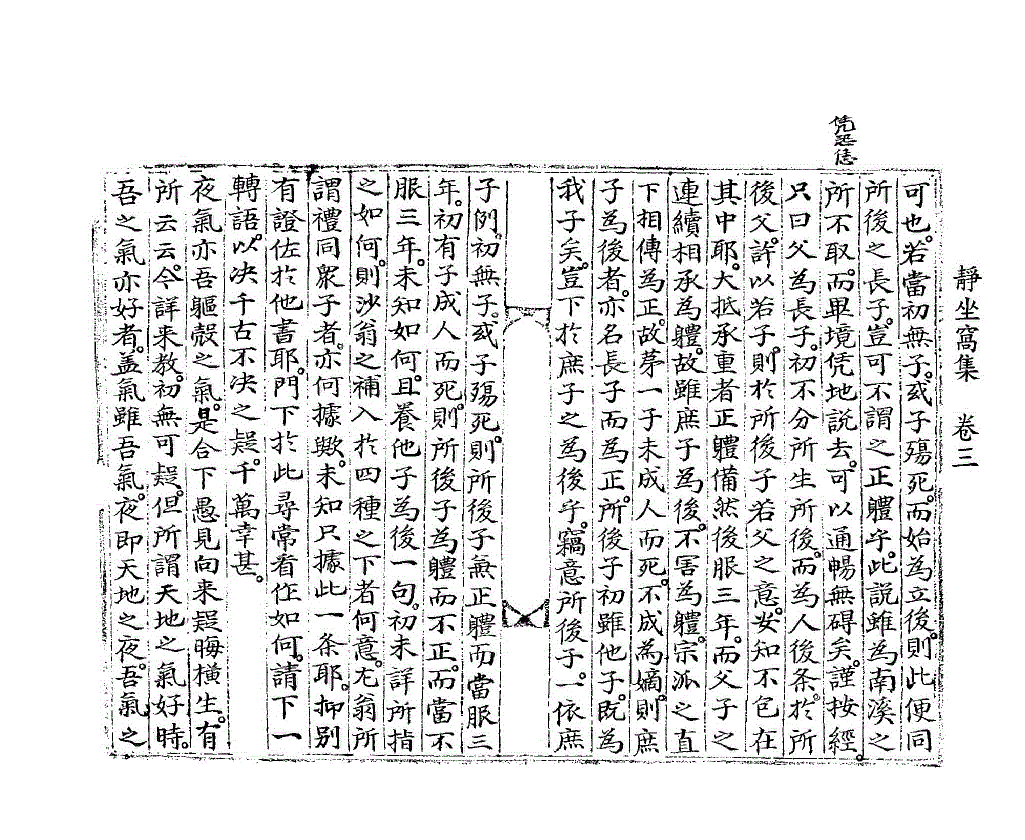 可也。若当初无子。或子殇死。而始为立后。则此便同所后之长子。岂可不谓之正体乎。此说虽为南溪之所不取。而毕境凭(凭。恐恁。)地说去。可以通畅无碍矣。谨按经。只曰父为长子。初不分所生所后。而为人后条。于所后父。许以若子。则于所后子若父之意。安知不包在其中耶。大抵承重者正体备然后服三年。而父子之连续相承为体。故虽庶子为后。不害为体。宗派之直下相传为正。故第一子未成人而死。不成为嫡。则庶子为后者。亦名长子而为正。所后子初虽他子。既为我子矣。岂下于庶子之为后乎。窃意所后子。一依庶子例。初无子。或子殇死。则所后子兼正体而当服三年。初有子成人而死。则所后子为体而不正。而当不服三年。未知如何。且养他子为后一句。初未详所指之如何。则沙翁之补入于四种之下者何意。尤翁所谓礼同众子者。亦何据欤。未知只据此一条耶。抑别有證佐于他书耶。门下于此寻常看作如何。请下一转语。以决千古不决之疑。千万幸甚。
可也。若当初无子。或子殇死。而始为立后。则此便同所后之长子。岂可不谓之正体乎。此说虽为南溪之所不取。而毕境凭(凭。恐恁。)地说去。可以通畅无碍矣。谨按经。只曰父为长子。初不分所生所后。而为人后条。于所后父。许以若子。则于所后子若父之意。安知不包在其中耶。大抵承重者正体备然后服三年。而父子之连续相承为体。故虽庶子为后。不害为体。宗派之直下相传为正。故第一子未成人而死。不成为嫡。则庶子为后者。亦名长子而为正。所后子初虽他子。既为我子矣。岂下于庶子之为后乎。窃意所后子。一依庶子例。初无子。或子殇死。则所后子兼正体而当服三年。初有子成人而死。则所后子为体而不正。而当不服三年。未知如何。且养他子为后一句。初未详所指之如何。则沙翁之补入于四种之下者何意。尤翁所谓礼同众子者。亦何据欤。未知只据此一条耶。抑别有證佐于他书耶。门下于此寻常看作如何。请下一转语。以决千古不决之疑。千万幸甚。夜气亦吾躯壳之气。是合下愚见向来疑晦横生。有所云云。今详来教。初无可疑。但所谓天地之气好时。吾之气亦好者。盖气虽吾气。夜即天地之夜。吾气之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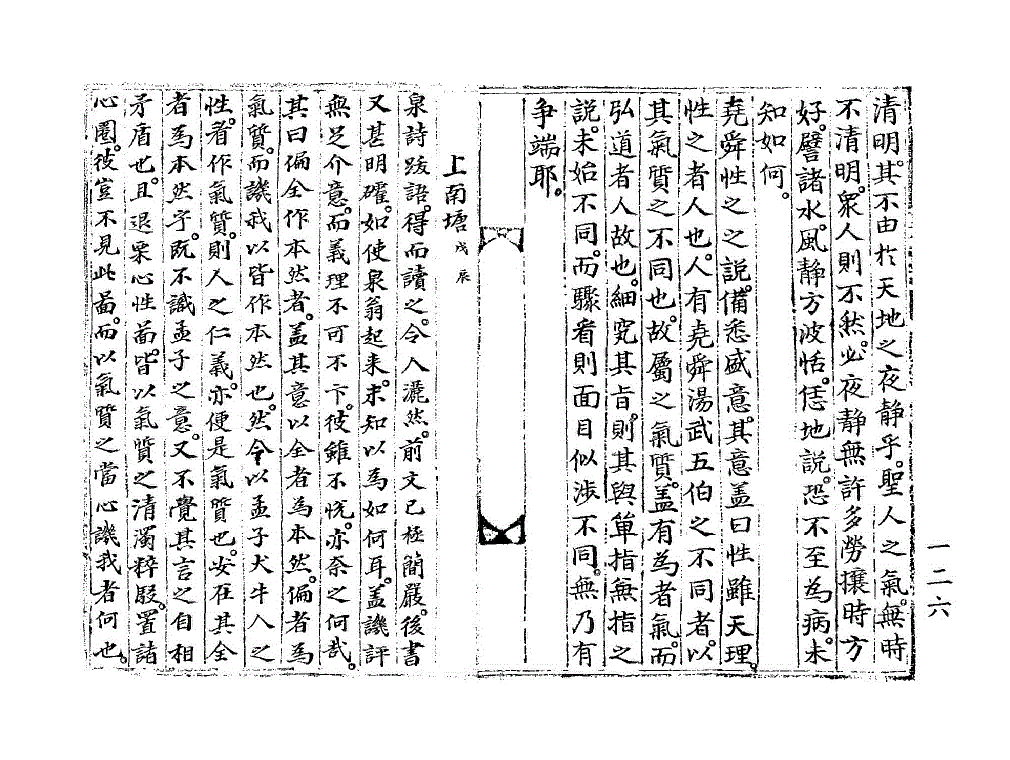 清明。其不由于天地之夜静乎。圣人之气。无时不清明。众人则不然。必夜静无许多劳攘时方好。譬诸水。风静方波恬。恁地说。恐不至为病。未知如何。
清明。其不由于天地之夜静乎。圣人之气。无时不清明。众人则不然。必夜静无许多劳攘时方好。譬诸水。风静方波恬。恁地说。恐不至为病。未知如何。尧舜性之之说。备悉盛意。其意盖曰性虽天理。性之者人也。人有尧舜汤武五伯之不同者。以其气质之不同也。故属之气质。盖有为者气。而弘道者人故也。细究其旨。则其与单指兼指之说。未始不同。而骤看则面目似涉不同。无乃有争端耶。
上南塘(戊辰)
泉诗跋语。得而读之。令人洒然。前文已极简严。后书又甚明礭。如使泉翁起来。未知以为如何耳。盖讥评无足介意。而义理不可不卞。彼虽不悦。亦奈之何哉。其曰偏全作本然者。盖其意以全者为本然。偏者为气质。而讥我以皆作本然也。然今以孟子犬牛人之性。看作气质。则人之仁义。亦便是气质也。安在其全者为本然乎。既不识孟子之意。又不觉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且退栗心性啚。皆以气质之清浊粹驳。置诸心圈。彼岂不见此啚。而以气质之当心讥我者何也。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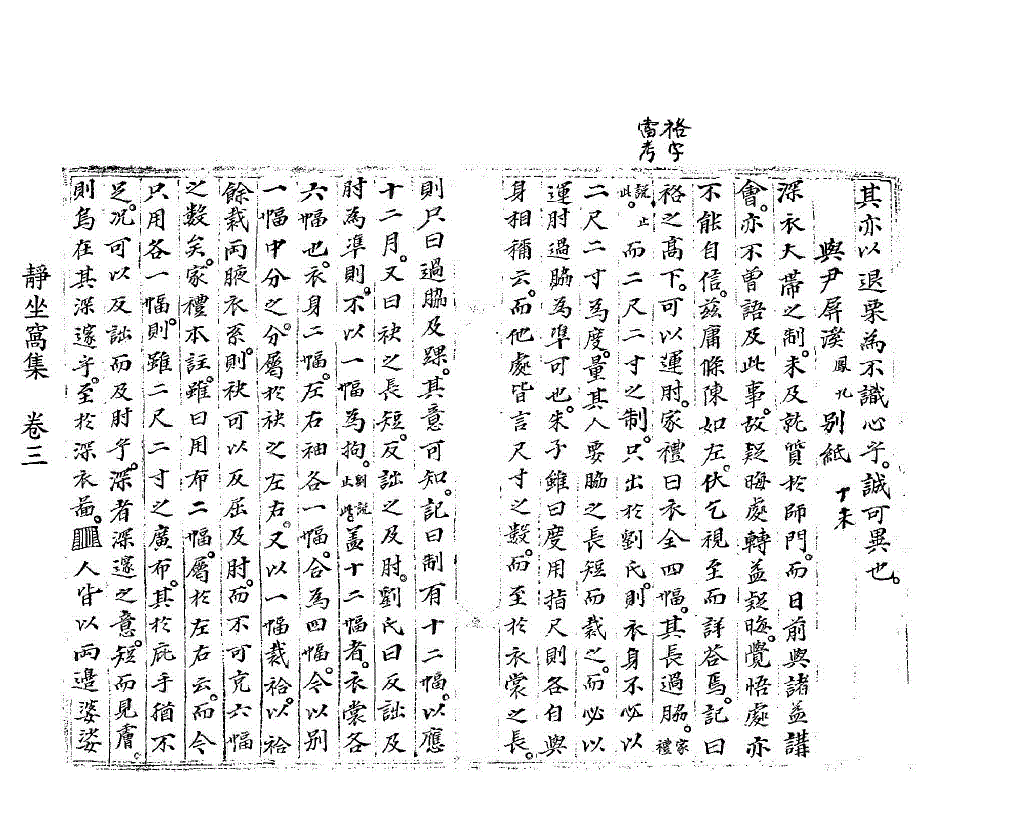 其亦以退栗为不识心乎。诚可异也。
其亦以退栗为不识心乎。诚可异也。与尹屏溪(凤九)别纸(丁未)
深衣大带之制。未及就质于师门。而日前与诸益讲会。亦不曾语及此事。故疑晦处转益疑晦。觉悟处亦不能自信。玆庸条陈如左。伏乞视至而详答焉。记曰袼(袼字。当考。)之高下。可以运肘。家礼曰衣全四幅。其长过胁。(家礼说止此。)而二尺二寸之制。只出于刘氏。则衣身不必以二尺二寸为度。量其人要胁之长短而裁之。而必以运肘过胁为准可也。朱子虽曰度用指尺则各自与身相称云。而他处皆言尺寸之数。而至于衣裳之长。则只曰过胁及踝。其意可知。记曰制有十二幅。以应十二月。又曰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刘氏曰反诎及肘为准则。不以一幅为拘。(刘说止此。)盖十二幅者。衣裳各六幅也。衣身二幅。左右袖各一幅。合为四幅。今以别一幅中分之。分属于袂之左右。又以一幅裁袷。以袷馀裁两腋衣系。则袂可以反屈及肘。而不可充六幅之数矣。家礼本注。虽曰用布二幅。属于左右云。而今只用各一幅。则虽二尺二寸之广布。其于庇手犹不足。况可以反诎而及肘乎。深者深邃之意。短而见肤。则乌在其深邃乎。至于深衣啚。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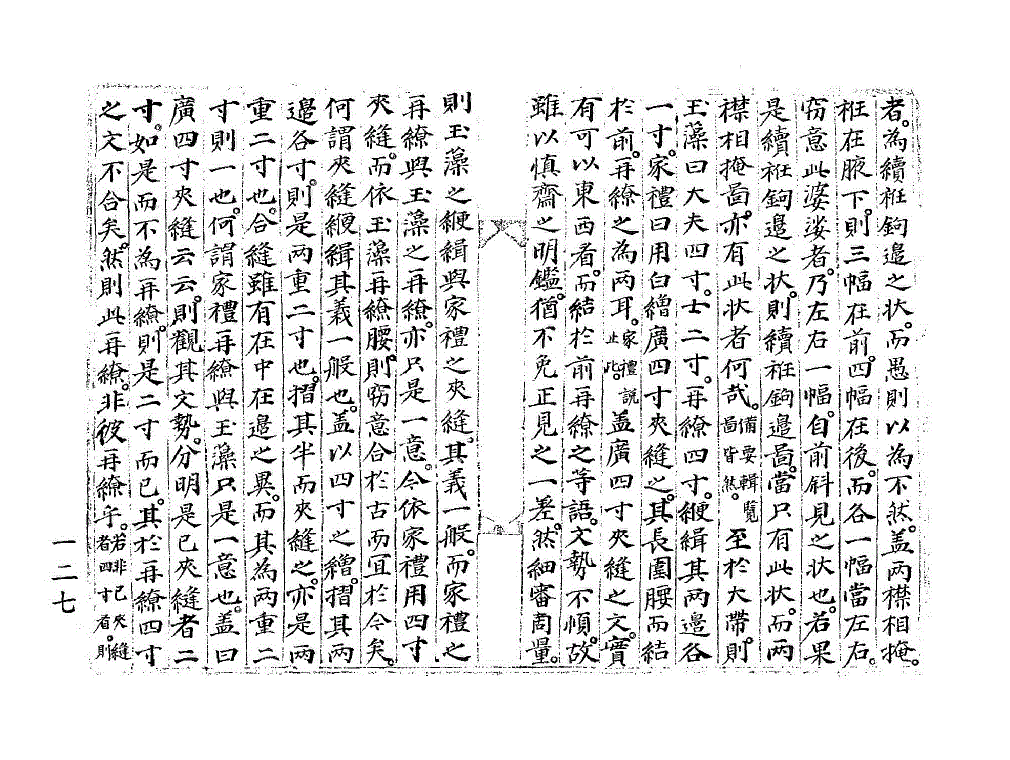 者。为续衽钩边之状。而愚则以为不然。盖两襟相掩。衽在腋下。则三幅在前。四幅在后。而各一幅当左右。窃意此婆娑者。乃左右一幅。自前斜见之状也。若果是续衽钩边之状。则续衽钩边啚。当只有此状。而两襟相掩啚。亦有此状者何哉。(备要辑览啚皆然。)至于大带。则玉藻曰大夫四寸。士二寸。再缭四寸。缏缉其两边各一寸。家礼曰用白缯广四寸夹缝之。其长围腰而结于前。再缭之为两耳。(家礼说止此。)盖广四寸夹缝之文。实有可以东西看。而结于前再缭之等语。文势不㥧。故虽以慎斋之明鉴。犹不免正见之一差。然细审商量。则玉藻之缏缉与家礼之夹缝。其义一般。而家礼之再缭与玉藻之再缭。亦只是一意。今依家礼用四寸夹缝。而依玉藻再缭腰。则窃意合于古而宜于今矣。何谓夹缝缏缉其义一般也。盖以四寸之缯。摺其两边各寸。则是两重二寸也。摺其半而夹缝之。亦是两重二寸也。合缝虽有在中在边之异。而其为两重二寸则一也。何谓家礼再缭与玉藻只是一意也。盖曰广四寸夹缝云云。则观其文势。分明是已夹缝者二寸。如是而不为再缭。则是二寸而已。其于再缭四寸之文不合矣。然则此再缭。非彼再缭乎。(若非已夹缝者四寸看。则
者。为续衽钩边之状。而愚则以为不然。盖两襟相掩。衽在腋下。则三幅在前。四幅在后。而各一幅当左右。窃意此婆娑者。乃左右一幅。自前斜见之状也。若果是续衽钩边之状。则续衽钩边啚。当只有此状。而两襟相掩啚。亦有此状者何哉。(备要辑览啚皆然。)至于大带。则玉藻曰大夫四寸。士二寸。再缭四寸。缏缉其两边各一寸。家礼曰用白缯广四寸夹缝之。其长围腰而结于前。再缭之为两耳。(家礼说止此。)盖广四寸夹缝之文。实有可以东西看。而结于前再缭之等语。文势不㥧。故虽以慎斋之明鉴。犹不免正见之一差。然细审商量。则玉藻之缏缉与家礼之夹缝。其义一般。而家礼之再缭与玉藻之再缭。亦只是一意。今依家礼用四寸夹缝。而依玉藻再缭腰。则窃意合于古而宜于今矣。何谓夹缝缏缉其义一般也。盖以四寸之缯。摺其两边各寸。则是两重二寸也。摺其半而夹缝之。亦是两重二寸也。合缝虽有在中在边之异。而其为两重二寸则一也。何谓家礼再缭与玉藻只是一意也。盖曰广四寸夹缝云云。则观其文势。分明是已夹缝者二寸。如是而不为再缭。则是二寸而已。其于再缭四寸之文不合矣。然则此再缭。非彼再缭乎。(若非已夹缝者四寸看。则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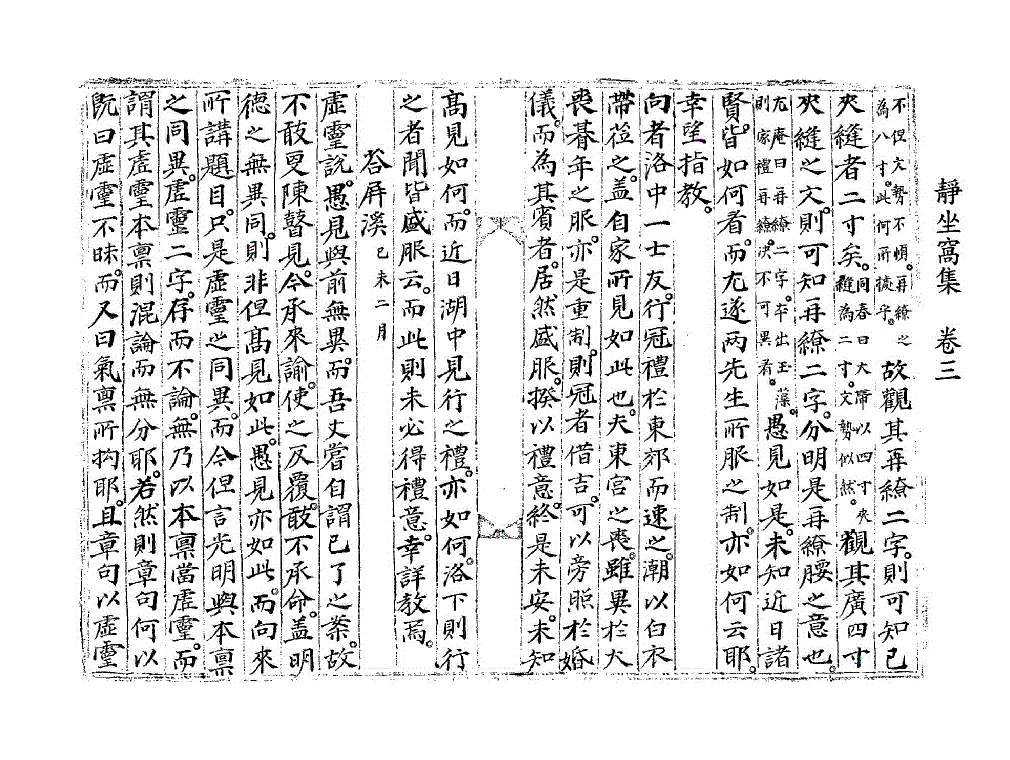 不但文势不㥧。再缭之为八寸。此何所据乎。)故观其再缭二字。则可知已夹缝者二寸矣。(同春曰大带以四寸夹缝为二寸。文势似然。)观其广四寸夹缝之文。则可知再缭二字。分明是再缭腰之意也。(尤庵曰再缭二字。本出玉藻。则家礼再缭。决不可异看。)愚见如是。未知近日诸贤。皆如何看。而尤遂两先生所服之制。亦如何云耶。幸望指教。
不但文势不㥧。再缭之为八寸。此何所据乎。)故观其再缭二字。则可知已夹缝者二寸矣。(同春曰大带以四寸夹缝为二寸。文势似然。)观其广四寸夹缝之文。则可知再缭二字。分明是再缭腰之意也。(尤庵曰再缭二字。本出玉藻。则家礼再缭。决不可异看。)愚见如是。未知近日诸贤。皆如何看。而尤遂两先生所服之制。亦如何云耶。幸望指教。向者洛中一士友。行冠礼于东郊而速之。潮以白衣带莅之。盖自家所见如此也。夫东宫之丧。虽异于大丧期年之服。亦是重制。则冠者借吉。可以旁照于婚仪。而为其宾者。居然盛服。揆以礼意。终是未安。未知高见如何。而近日湖中见行之礼。亦如何。洛下则行之者闻皆盛服云。而此则未必得礼意。幸详教焉。
答屏溪(己未二月)
虚灵说。愚见与前无异。而吾丈尝自谓已了之案。故不敢更陈瞽见。今承来谕。使之反覆。敢不承命。盖明德之无异同。则非但高见如此。愚见亦如此。而向来所讲题目。只是虚灵之同异。而今但言光明与本禀之同异。虚灵二字。存而不论。无乃以本禀当虚灵。而谓其虚灵本禀则混论而无分耶。若然则章句何以既曰虚灵不昧。而又曰气禀所拘耶。且章句以虚灵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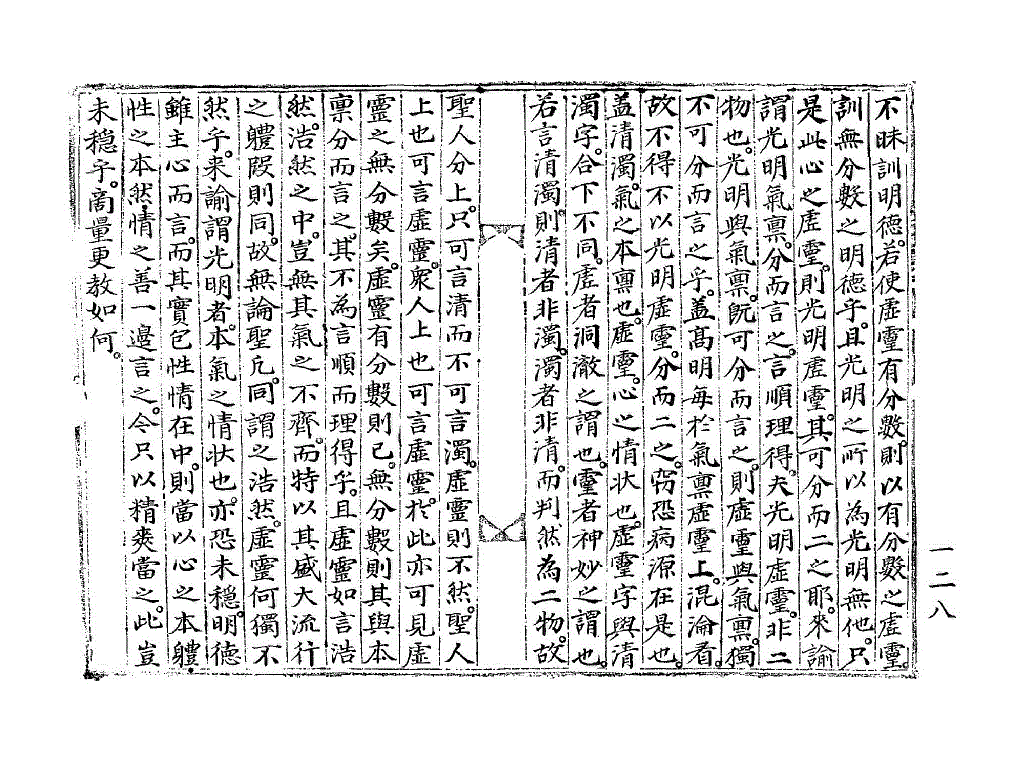 不昧训明德。若使虚灵有分数。则以有分数之虚灵。训无分数之明德乎。且光明之所以为光明无他。只是此心之虚灵。则光明虚灵。其可分而二之耶。来谕谓光明气禀。分而言之。言顺理得。夫光明虚灵。非二物也。光明与气禀。既可分而言之。则虚灵与气禀。独不可分而言之乎。盖高明每于气禀虚灵上。混沦看。故不得不以光明虚灵。分而二之。窃恐病源在是也。盖清浊。气之本禀也。虚灵。心之情状也。虚灵字与清浊字。合下不同。虚者洞澈之谓也。灵者神妙之谓也。若言清浊。则清者非浊。浊者非清。而判然为二物。故圣人分上。只可言清而不可言浊。虚灵则不然。圣人上也可言虚灵。众人上也可言虚灵。于此亦可见虚灵之无分数矣。虚灵有分数则已。无分数则其与本禀分而言之。其不为言顺而理得乎。且虚灵如言浩然。浩然之中。岂无其气之不齐。而特以其盛大流行之体段则同。故无论圣凡。同谓之浩然。虚灵何独不然乎。来谕谓光明者。本气之情状也。亦恐未稳。明德虽主心而言。而其实包性情在中。则当以心之本体,性之本然,情之善一边言之。今只以精爽当之。此岂未稳乎。商量更教如何。
不昧训明德。若使虚灵有分数。则以有分数之虚灵。训无分数之明德乎。且光明之所以为光明无他。只是此心之虚灵。则光明虚灵。其可分而二之耶。来谕谓光明气禀。分而言之。言顺理得。夫光明虚灵。非二物也。光明与气禀。既可分而言之。则虚灵与气禀。独不可分而言之乎。盖高明每于气禀虚灵上。混沦看。故不得不以光明虚灵。分而二之。窃恐病源在是也。盖清浊。气之本禀也。虚灵。心之情状也。虚灵字与清浊字。合下不同。虚者洞澈之谓也。灵者神妙之谓也。若言清浊。则清者非浊。浊者非清。而判然为二物。故圣人分上。只可言清而不可言浊。虚灵则不然。圣人上也可言虚灵。众人上也可言虚灵。于此亦可见虚灵之无分数矣。虚灵有分数则已。无分数则其与本禀分而言之。其不为言顺而理得乎。且虚灵如言浩然。浩然之中。岂无其气之不齐。而特以其盛大流行之体段则同。故无论圣凡。同谓之浩然。虚灵何独不然乎。来谕谓光明者。本气之情状也。亦恐未稳。明德虽主心而言。而其实包性情在中。则当以心之本体,性之本然,情之善一边言之。今只以精爽当之。此岂未稳乎。商量更教如何。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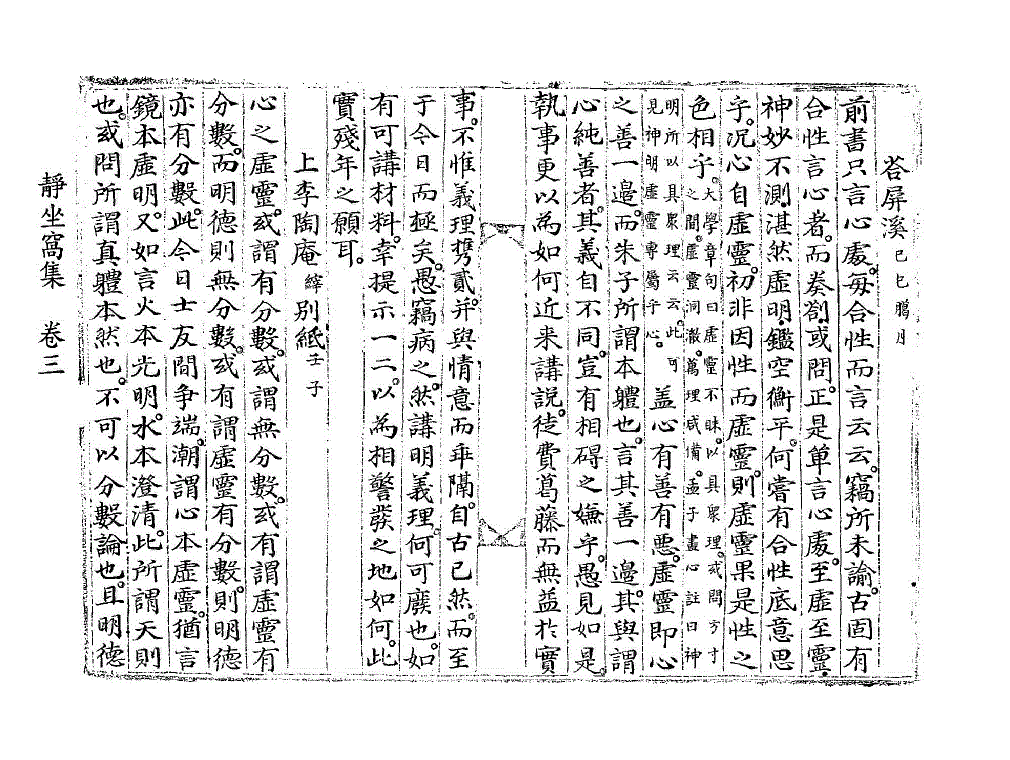 答屏溪(己巳臈月)
答屏溪(己巳臈月)前书只言心处。每合性而言云云。窃所未谕。古固有合性言心者。而奏劄,或问。正是单言心处。至虚至灵,神妙不测,湛然虚明,鉴空衡平。何尝有合性底意思乎。况心自虚灵。初非因性而虚灵。则虚灵果是性之色相乎。(大学章句曰虚灵不昧。以具众理。或问方寸之间。虚灵洞澈。万理咸备。孟子尽心注曰神明所以具众理云云。此可见神明虚灵专属乎心。)盖心有善有恶。虚灵即心之善一边。而朱子所谓本体也。言其善一边。其与谓心纯善者。其义自不同。岂有相碍之嫌乎。愚见如是。执事更以为如何近来讲说。徒费葛藤而无益于实事。不惟义理携贰。并与情意而乖隔。自古已然。而至于今日而极矣。愚窃病之。然讲明义理。何可废也。如有可讲材料。幸提示一二。以为相警发之地如何。此实残年之愿耳。
上李陶庵(縡)别纸(壬子)
心之虚灵。或谓有分数。或谓无分数。或有谓虚灵有分数。而明德则无分数。或有谓虚灵有分数。则明德亦有分数。此今日士友间争端。潮谓心本虚灵。犹言镜本虚明。又如言火本光明。水本澄清。此所谓天则也。或问所谓真体本然也。不可以分数论也。且明德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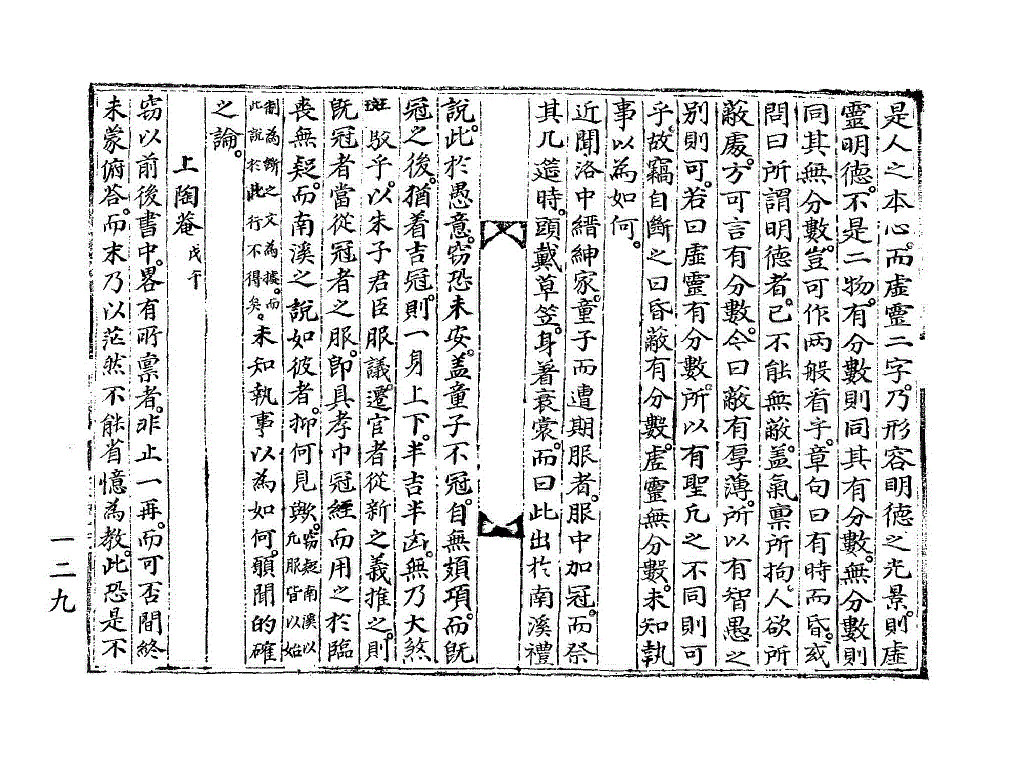 是人之本心。而虚灵二字。乃形容明德之光景。则虚灵明德。不是二物。有分数则同其有分数。无分数则同其无分数。岂可作两般看乎。章句曰有时而昏。或问曰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盖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处。方可言有分数。今曰蔽有厚薄。所以有智愚之别则可。若曰虚灵有分数。所以有圣凡之不同则可乎。故窃自断之曰昏蔽有分数。虚灵无分数。未知执事以为如何。
是人之本心。而虚灵二字。乃形容明德之光景。则虚灵明德。不是二物。有分数则同其有分数。无分数则同其无分数。岂可作两般看乎。章句曰有时而昏。或问曰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盖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处。方可言有分数。今曰蔽有厚薄。所以有智愚之别则可。若曰虚灵有分数。所以有圣凡之不同则可乎。故窃自断之曰昏蔽有分数。虚灵无分数。未知执事以为如何。近闻洛中缙绅家。童子而遭期服者。服中加冠。而祭其几筵时。头戴草笠。身着衰裳。而曰此出于南溪礼说。此于愚意。窃恐未安。盖童子不冠。自无頍项。而既冠之后。犹着吉冠。则一身上下。半吉半凶。无乃大煞斑驳乎。以朱子君臣服议。迁官者从新之义推之。则既冠者当从冠者之服。即具孝巾冠经而用之于临丧无疑。而南溪之说如彼者。抑何见欤。(窃疑南溪以凡服皆以始制为断之文为据。而此说于此行不得矣。)未知执事以为如何。愿闻的确之论。
上陶庵(戊午)
窃以前后书中。略有所禀者。非止一再。而可否间终未蒙俯答。而末乃以茫然不能省忆为教。此恐是不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0H 页
 屑之教诲也。不胜瞿然之至。然窃听于师友间。门下于此等酬酢。深所厌薄。诚然则无或有异于朱子法门耶。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固古今之通患。而专践履者。遂以讲学为无益者。亦岂非朱先生所深戒乎。大抵讲学践履。互相资益。而初不相妨。矫时学之弊。而勉人以践履则可也。若以讲学为咎。而欲遂废之。则不几于因噎而废食(因讲学而云。因噎废食。为世所讳。今录此书。未知如何。)者乎。虽曰知易。而真知最难。天下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此所以学贵于真知也。上世义理素明。故善人多而恶人少。后世义理不明。故恶人多而善人少。任世教者。当以明义理为事。夫讲学者。明义理事也。欲明义理。舍讲学而何以哉。幸毋以讲学为无益。而必使义理大明于世。如何如何。疑当思问。倾倒至此。极知僭踰。不任惶悚。
屑之教诲也。不胜瞿然之至。然窃听于师友间。门下于此等酬酢。深所厌薄。诚然则无或有异于朱子法门耶。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固古今之通患。而专践履者。遂以讲学为无益者。亦岂非朱先生所深戒乎。大抵讲学践履。互相资益。而初不相妨。矫时学之弊。而勉人以践履则可也。若以讲学为咎。而欲遂废之。则不几于因噎而废食(因讲学而云。因噎废食。为世所讳。今录此书。未知如何。)者乎。虽曰知易。而真知最难。天下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此所以学贵于真知也。上世义理素明。故善人多而恶人少。后世义理不明。故恶人多而善人少。任世教者。当以明义理为事。夫讲学者。明义理事也。欲明义理。舍讲学而何以哉。幸毋以讲学为无益。而必使义理大明于世。如何如何。疑当思问。倾倒至此。极知僭踰。不任惶悚。上陶庵(己未八月)
日者所禀。获赐反覆。深荷不外。湖中一种心纯善之说。愚尝习闻之矣。盖主此说者。对人辄说心是至好底物。而亦尝曰心者非理非气。自有一个神底物事。此则分明是禅家所谓心。非吾儒所谓心也。向来涂听途说。妄疑长者于此。亦未免正见之一累。今承下教。乃知盛意所在。与彼一种之说。煞有不同者矣。但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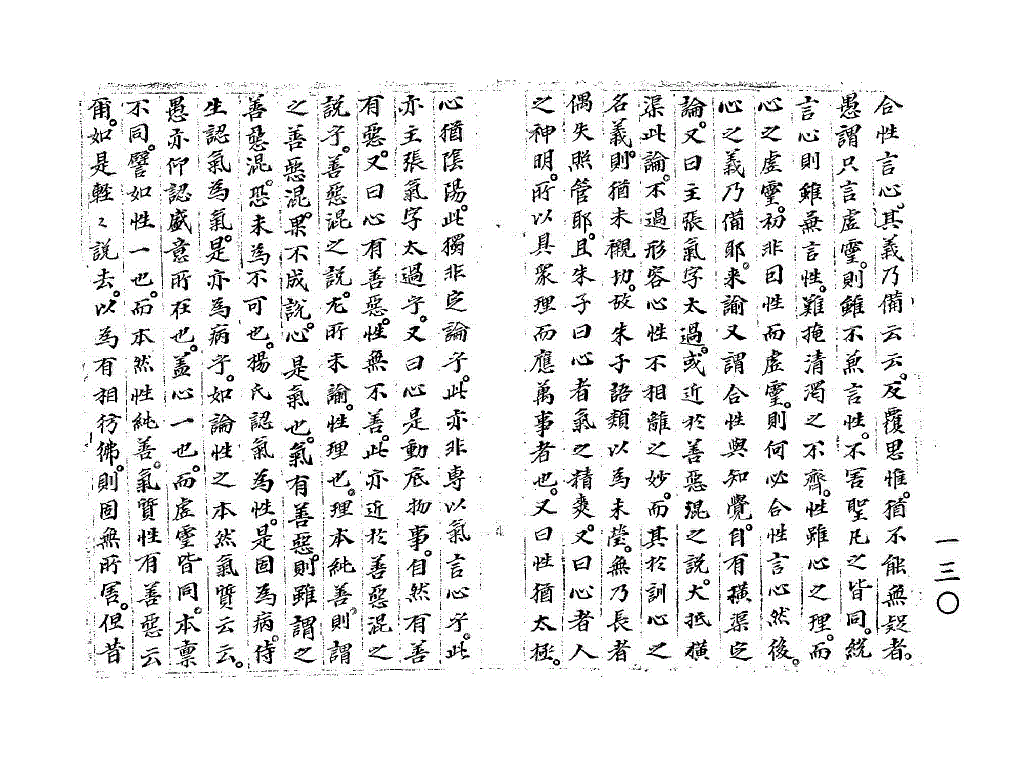 合性言心。其义乃备云云。反覆思惟。犹不能无疑者。愚谓只言虚灵。则虽不兼言性。不害圣凡之皆同。统言心则虽兼言性。难掩清浊之不齐。性虽心之理。而心之虚灵。初非因性而虚灵。则何必合性言心然后。心之义乃备耶。来谕又谓合性与知觉。自有横渠定论。又曰主张气字太过。或近于善恶混之说。大抵横渠此论。不过形容心性不相离之妙。而其于训心之名义。则犹未衬切。故朱子语类以为未莹。无乃长者偶失照管耶。且朱子曰心者气之精爽。又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又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此独非定论乎。此亦非专以气言心乎。此亦主张气字太过乎。又曰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有恶。又曰心有善恶。性无不善。此亦近于善恶混之说乎。善恶混之说。尤所未谕。性理也。理本纯善。则谓之善恶混。果不成说。心是气也。气有善恶。则虽谓之善恶混。恐未为不可也。杨氏认气为性。是固为病。侍生认气为气。是亦为病乎。如论性之本然气质云云。愚亦仰认盛意所在也。盖心一也。而虚灵皆同。本禀不同。譬如性一也。而本然性纯善。气质性有善恶云尔。如是轻轻说去。以为有相彷佛。则固无所害。但昔
合性言心。其义乃备云云。反覆思惟。犹不能无疑者。愚谓只言虚灵。则虽不兼言性。不害圣凡之皆同。统言心则虽兼言性。难掩清浊之不齐。性虽心之理。而心之虚灵。初非因性而虚灵。则何必合性言心然后。心之义乃备耶。来谕又谓合性与知觉。自有横渠定论。又曰主张气字太过。或近于善恶混之说。大抵横渠此论。不过形容心性不相离之妙。而其于训心之名义。则犹未衬切。故朱子语类以为未莹。无乃长者偶失照管耶。且朱子曰心者气之精爽。又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又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此独非定论乎。此亦非专以气言心乎。此亦主张气字太过乎。又曰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有恶。又曰心有善恶。性无不善。此亦近于善恶混之说乎。善恶混之说。尤所未谕。性理也。理本纯善。则谓之善恶混。果不成说。心是气也。气有善恶。则虽谓之善恶混。恐未为不可也。杨氏认气为性。是固为病。侍生认气为气。是亦为病乎。如论性之本然气质云云。愚亦仰认盛意所在也。盖心一也。而虚灵皆同。本禀不同。譬如性一也。而本然性纯善。气质性有善恶云尔。如是轻轻说去。以为有相彷佛。则固无所害。但昔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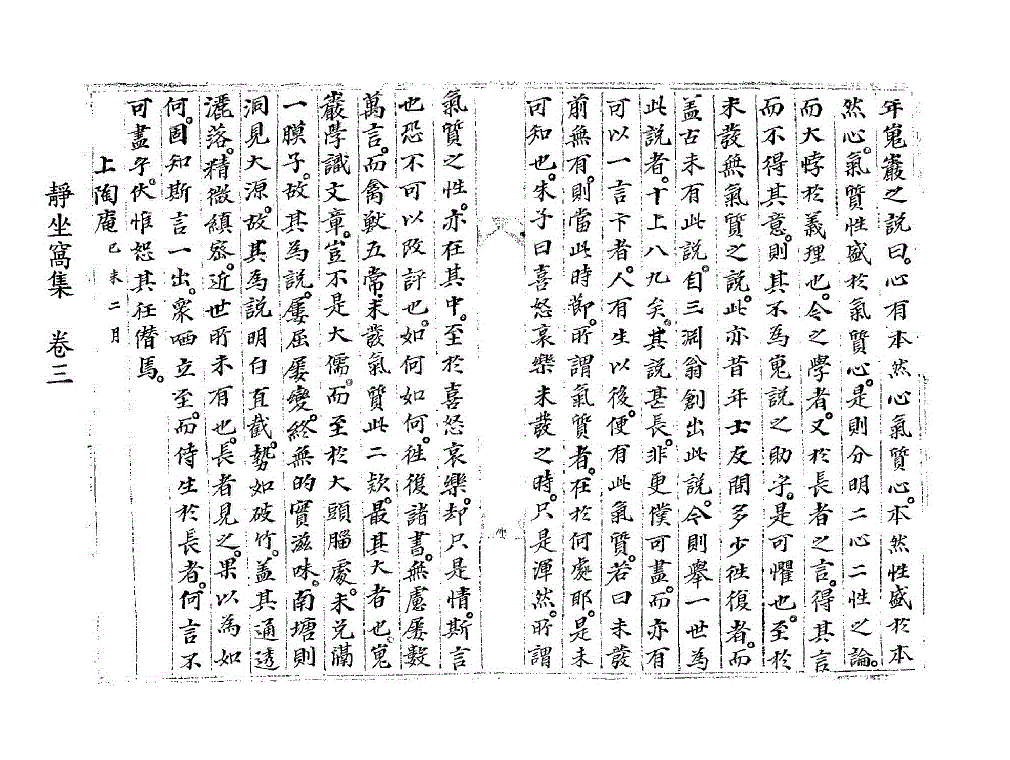 年嵬岩之说曰。心有本然心气质心。本然性盛于本然心。气质性盛于气质心。是则分明二心二性之论。而大悖于义理也。今之学者。又于长者之言。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则其不为嵬说之助乎。是可惧也。至于未发无气质之说。此亦昔年士友间多少往复者。而盖古未有此说。自三渊翁创出此说。今则举一世为此说者。十上八九矣。其说甚长。非更仆可尽。而亦有可以一言卞者。人有生以后。便有此气质。若曰未发前无有。则当此时节。所谓气质者。在于何处耶。是未可知也。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在其中。至于喜怒哀乐。却只是情。斯言也恐不可以改评也。如何如何。往复诸书。无虑屡数万言。而禽兽五常,未发气质此二款。最其大者也。嵬岩学识文章。岂不是大儒。而至于大头脑处。未免隔一膜子。故其为说。屡屈屡变。终无的实滋味。南塘则洞见大源。故其为说明白直截。势如破竹。盖其通透洒落。精微缜密。近世所未有也。长者见之。果以为如何。固知斯言一出。众哂立至。而侍生于长者。何言不可尽乎。伏惟恕其狂僭焉。
年嵬岩之说曰。心有本然心气质心。本然性盛于本然心。气质性盛于气质心。是则分明二心二性之论。而大悖于义理也。今之学者。又于长者之言。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则其不为嵬说之助乎。是可惧也。至于未发无气质之说。此亦昔年士友间多少往复者。而盖古未有此说。自三渊翁创出此说。今则举一世为此说者。十上八九矣。其说甚长。非更仆可尽。而亦有可以一言卞者。人有生以后。便有此气质。若曰未发前无有。则当此时节。所谓气质者。在于何处耶。是未可知也。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在其中。至于喜怒哀乐。却只是情。斯言也恐不可以改评也。如何如何。往复诸书。无虑屡数万言。而禽兽五常,未发气质此二款。最其大者也。嵬岩学识文章。岂不是大儒。而至于大头脑处。未免隔一膜子。故其为说。屡屈屡变。终无的实滋味。南塘则洞见大源。故其为说明白直截。势如破竹。盖其通透洒落。精微缜密。近世所未有也。长者见之。果以为如何。固知斯言一出。众哂立至。而侍生于长者。何言不可尽乎。伏惟恕其狂僭焉。上陶庵(己未二月)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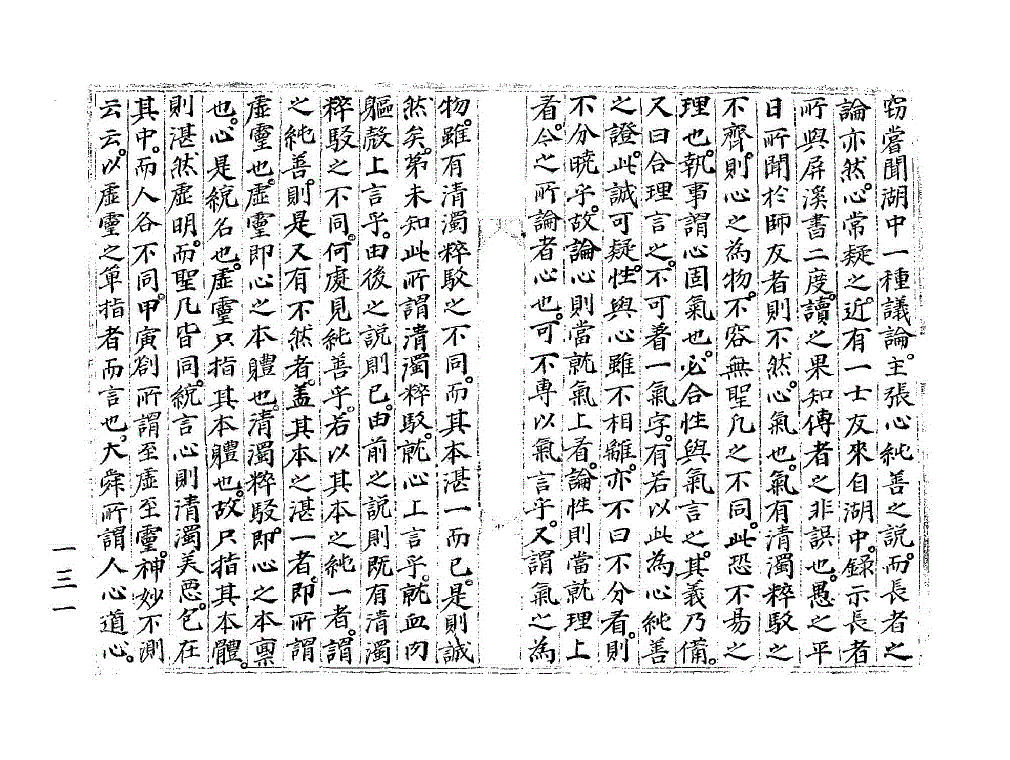 窃尝闻湖中一种议论。主张心纯善之说。而长者之论亦然。心常疑之。近有一士友来自湖中。录示长者所与屏溪书二度。读之果知传者之非误也。愚之平日所闻于师友者则不然。心气也。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则心之为物。不容无圣凡之不同。此恐不易之理也。执事谓心固气也。必合性与气言之。其义乃备。又曰合理言之。不可着一气字。有若以此为心纯善之證。此诚可疑。性与心虽不相离。亦不曰不分看。则不分晓乎。故论心则当就气上看。论性则当就理上看。今之所论者心也。可不专以气言乎。又谓气之为物。虽有清浊粹驳之不同。而其本湛一而已。是则诚然矣。第未知此所谓清浊粹驳。就心上言乎。就血肉躯壳上言乎。由后之说则已。由前之说则既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何处见纯善乎。若以其本之纯一者。谓之纯善。则是又有不然者。盖其本之湛一者。即所谓虚灵也。虚灵即心之本体也。清浊粹驳。即心之本禀也。心是统名也。虚灵只指其本体也。故只指其本体。则湛然虚明。而圣凡皆同。统言心则清浊美恶。包在其中。而人各不同。甲寅劄所谓至虚至灵。神妙不测云云。以虚灵之单指者而言也。大舜所谓人心道心。
窃尝闻湖中一种议论。主张心纯善之说。而长者之论亦然。心常疑之。近有一士友来自湖中。录示长者所与屏溪书二度。读之果知传者之非误也。愚之平日所闻于师友者则不然。心气也。气有清浊粹驳之不齐。则心之为物。不容无圣凡之不同。此恐不易之理也。执事谓心固气也。必合性与气言之。其义乃备。又曰合理言之。不可着一气字。有若以此为心纯善之證。此诚可疑。性与心虽不相离。亦不曰不分看。则不分晓乎。故论心则当就气上看。论性则当就理上看。今之所论者心也。可不专以气言乎。又谓气之为物。虽有清浊粹驳之不同。而其本湛一而已。是则诚然矣。第未知此所谓清浊粹驳。就心上言乎。就血肉躯壳上言乎。由后之说则已。由前之说则既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何处见纯善乎。若以其本之纯一者。谓之纯善。则是又有不然者。盖其本之湛一者。即所谓虚灵也。虚灵即心之本体也。清浊粹驳。即心之本禀也。心是统名也。虚灵只指其本体也。故只指其本体。则湛然虚明。而圣凡皆同。统言心则清浊美恶。包在其中。而人各不同。甲寅劄所谓至虚至灵。神妙不测云云。以虚灵之单指者而言也。大舜所谓人心道心。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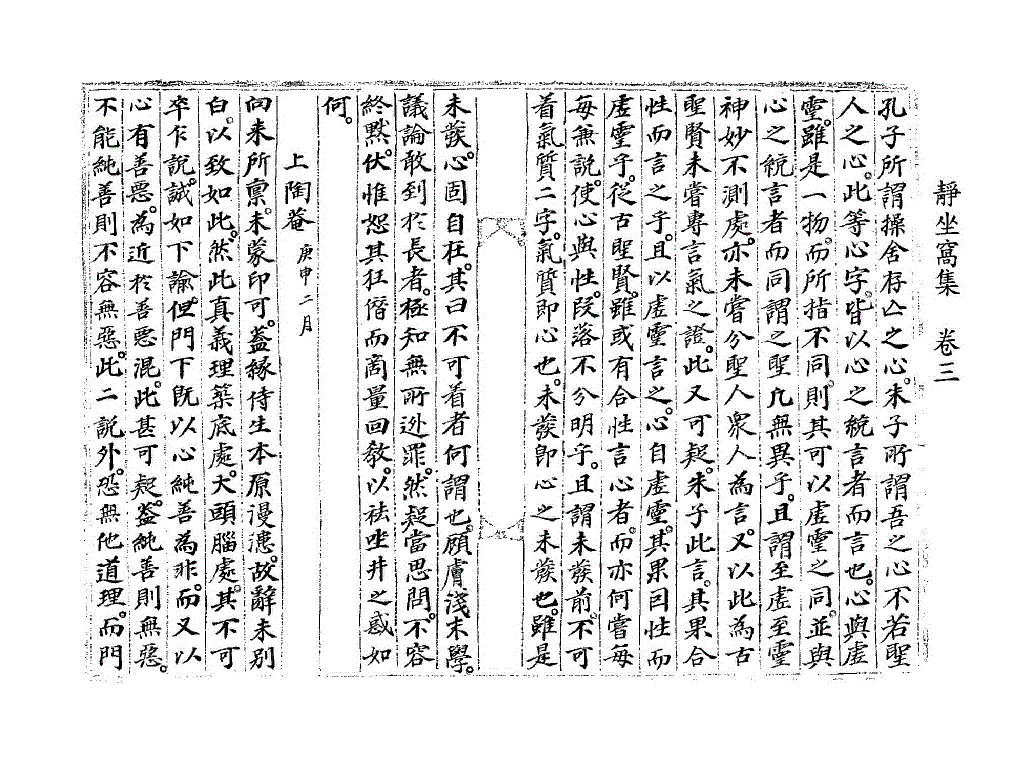 孔子所谓操舍存亡之心。朱子所谓吾之心不若圣人之心。此等心字。皆以心之统言者而言也。心与虚灵。虽是一物。而所指不同。则其可以虚灵之同。并与心之统言者而同谓之圣凡无异乎。且谓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处。亦未尝分圣人众人为言。又以此为古圣贤未尝专言气之證。此又可疑。朱子此言。其果合性而言之乎。且以虚灵言之。心自虚灵。其果因性而虚灵乎。从古圣贤。虽或有合性言心者。而亦何尝每每兼说。使心与性。段落不分明乎。且谓未发前。不可着气质二字。气质即心也。未发即心之未发也。虽是未发。心固自在。其曰不可着者何谓也。顾肤浅末学。议论敢到于长者。极知无所逃罪。然疑当思问。不容终默。伏惟恕其狂僭而商量回教。以祛坐井之惑如何。
孔子所谓操舍存亡之心。朱子所谓吾之心不若圣人之心。此等心字。皆以心之统言者而言也。心与虚灵。虽是一物。而所指不同。则其可以虚灵之同。并与心之统言者而同谓之圣凡无异乎。且谓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处。亦未尝分圣人众人为言。又以此为古圣贤未尝专言气之證。此又可疑。朱子此言。其果合性而言之乎。且以虚灵言之。心自虚灵。其果因性而虚灵乎。从古圣贤。虽或有合性言心者。而亦何尝每每兼说。使心与性。段落不分明乎。且谓未发前。不可着气质二字。气质即心也。未发即心之未发也。虽是未发。心固自在。其曰不可着者何谓也。顾肤浅末学。议论敢到于长者。极知无所逃罪。然疑当思问。不容终默。伏惟恕其狂僭而商量回教。以祛坐井之惑如何。上陶庵(庚申二月)
向来所禀。未蒙印可。盖缘侍生本原漫漶。故辞未别白。以致如此。然此真义理筑底处。大头脑处。其不可卒乍说。诚如下谕。但门下既以心纯善为非。而又以心有善恶。为近于善恶混。此甚可疑。盖纯善则无恶。不能纯善则不容无恶。此二说外。恐无他道理。而门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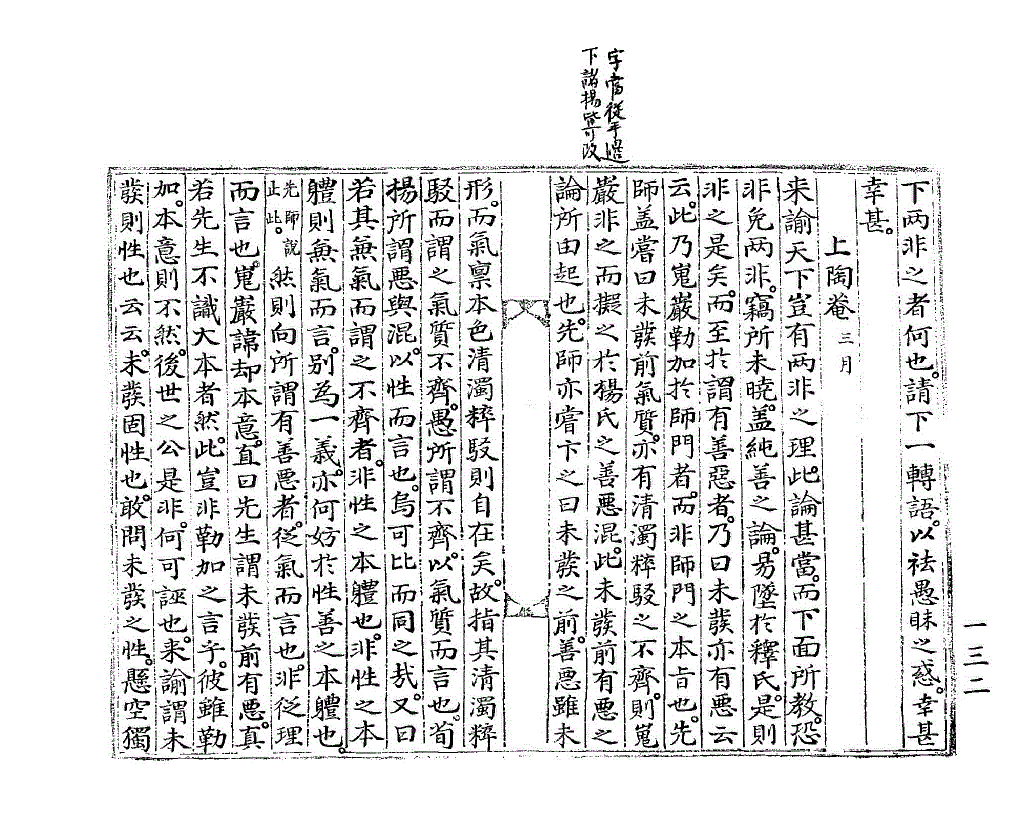 下两非之者何也。请下一转语。以祛愚昧之惑。幸甚幸甚。
下两非之者何也。请下一转语。以祛愚昧之惑。幸甚幸甚。上陶庵(三月)
来谕天下岂有两非之理。此论甚当。而下面所教。恐非免两非。窃所未晓。盖纯善之论。易坠于释氏。是则非之是矣。而至于谓有善恶者。乃曰未发亦有恶云云。此乃嵬岩勒加于师门者。而非师门之本旨也。先师盖尝曰未发前气质。亦有清浊粹驳之不齐。则嵬岩非之而拟之于杨(扬字。当从手边。以下诸扬。皆可改。)氏之善恶混。此未发前有恶之论所由起也。先师亦尝卞之曰未发之前。善恶虽未形。而气禀本色清浊粹驳则自在矣。故指其清浊粹驳而谓之气质不齐。愚所谓不齐。以气质而言也。荀扬所谓恶与混。以性而言也。乌可比而同之哉。又曰若其兼气而谓之不齐者。非性之本体也。非性之本体则兼气而言。别为一义。亦何妨于性善之本体也。(先师说止此。)然则向所谓有善恶者。从气而言也。非从理而言也。嵬岩讳却本意。直曰先生谓未发前有恶。真若先生不识大本者然。此岂非勒加之言乎。彼虽勒加。本意则不然。后世之公是非。何可诬也。来谕谓未发则性也云云。未发固性也。敢问未发之性。悬空独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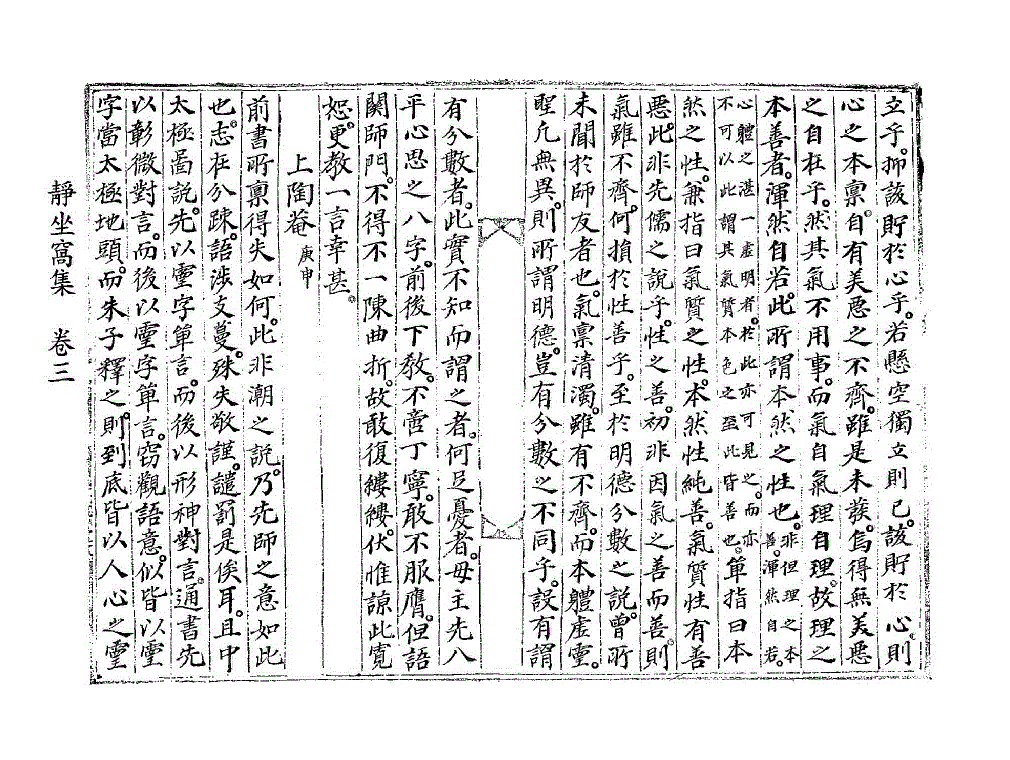 立乎。抑该贮于心乎。若悬空独立则已。该贮于心。则心之本禀。自有美恶之不齐。虽是未发。乌得无美恶之自在乎。然其气不用事。而气自气理自理。故理之本善者。浑然自若。此所谓本然之性也。(非但理之本善。浑然自若。心体之湛一虚明者。于此亦可见之。而亦不可以此谓其气质本色之至此皆善也。)单指曰本然之性。兼指曰气质之性。本然性纯善。气质性有善恶。此非先儒之说乎。性之善。初非因气之善而善。则气虽不齐。何损于性善乎。至于明德分数之说。曾所未闻于师友者也。气禀清浊。虽有不齐。而本体虚灵。圣凡无异。则所谓明德。岂有分数之不同乎。设有谓有分数者。此实不知而谓之者。何足忧者。毋主先入平心思之八字。前后下教。不啻丁宁。敢不服膺。但语关师门。不得不一陈曲折。故敢复缕缕。伏惟谅此宽恕。更教一言幸甚。
立乎。抑该贮于心乎。若悬空独立则已。该贮于心。则心之本禀。自有美恶之不齐。虽是未发。乌得无美恶之自在乎。然其气不用事。而气自气理自理。故理之本善者。浑然自若。此所谓本然之性也。(非但理之本善。浑然自若。心体之湛一虚明者。于此亦可见之。而亦不可以此谓其气质本色之至此皆善也。)单指曰本然之性。兼指曰气质之性。本然性纯善。气质性有善恶。此非先儒之说乎。性之善。初非因气之善而善。则气虽不齐。何损于性善乎。至于明德分数之说。曾所未闻于师友者也。气禀清浊。虽有不齐。而本体虚灵。圣凡无异。则所谓明德。岂有分数之不同乎。设有谓有分数者。此实不知而谓之者。何足忧者。毋主先入平心思之八字。前后下教。不啻丁宁。敢不服膺。但语关师门。不得不一陈曲折。故敢复缕缕。伏惟谅此宽恕。更教一言幸甚。上陶庵(庚申)
前书所禀得失如何。此非潮之说。乃先师之意如此也。志在分疏。语涉支蔓。殊失敬谨。谴罚是俟耳。且中太极啚说。先以灵字单言。而后以形神对言。通书先以彰微对言。而后以灵字单言。窃观语意。似皆以灵字当太极地头。而朱子释之。则到底皆以人心之灵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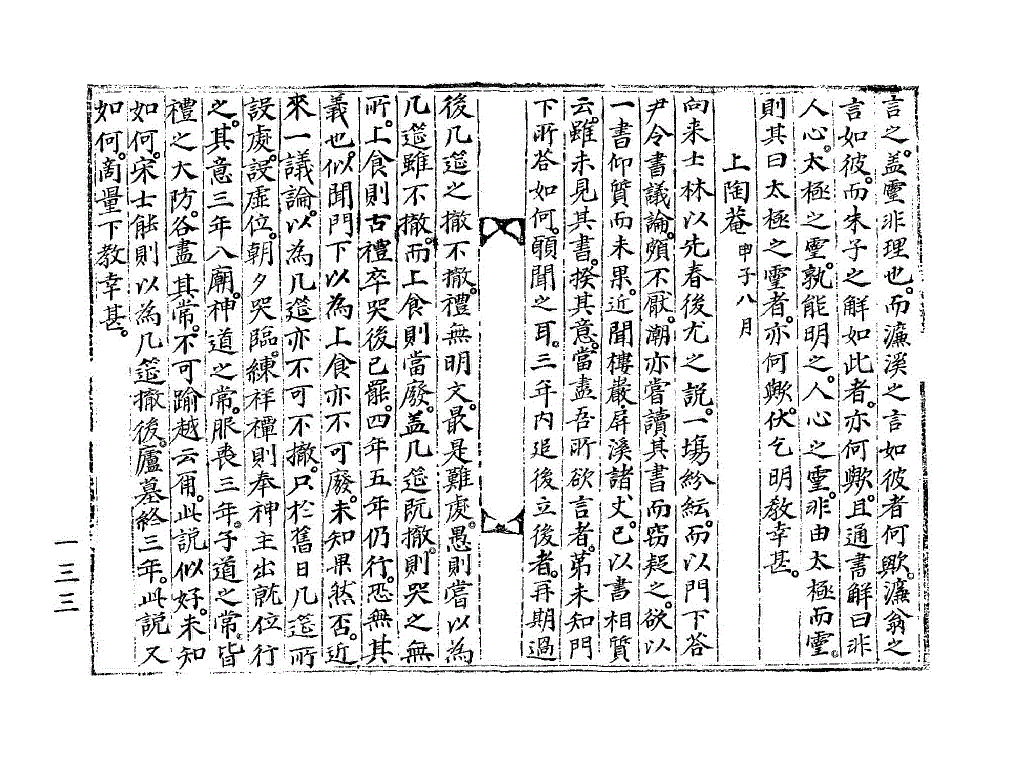 言之。盖灵非理也。而濂溪之言如彼者何欤。濂翁之言如彼。而朱子之解如此者。亦何欤。且通书解曰非人心。太极之灵。孰能明之。人心之灵。非由太极而灵。则其曰太极之灵者。亦何欤。伏乞明教幸甚。
言之。盖灵非理也。而濂溪之言如彼者何欤。濂翁之言如彼。而朱子之解如此者。亦何欤。且通书解曰非人心。太极之灵。孰能明之。人心之灵。非由太极而灵。则其曰太极之灵者。亦何欤。伏乞明教幸甚。上陶庵(甲子八月)
向来士林以先春后尤之说。一场纷纭。而以门下答尹令书议论。颇不厌。潮亦尝读其书而窃疑之。欲以一书仰质而未果。近闻楼岩,屏溪诸丈。已以书相质云。虽未见其书。揆其意。当尽吾所欲言者。第未知门下所答如何。愿闻之耳。三年内追后立后者。再期过后几筵之撤不撤。礼无明文。最是难处。愚则尝以为几筵虽不撤。而上食则当废。盖几筵既撤。则哭之无所。上食则古礼卒哭后已罢。四年五年仍行。恐无其义也。似闻门下以为上食亦不可废。未知果然否。近来一议论。以为几筵亦不可不撤。只于旧日几筵所设处。设虚位。朝夕哭临。练祥禫则奉神主出就位行之。其意三年入庙。神道之常。服丧三年。子道之常。皆礼之大防。各尽其常。不可踰越云尔。此说似好。未知如何。宋士能则以为几筵撤后。庐墓终三年。此说又如何。商量下教幸甚。
代牛渚院儒上陶庵
就白昨年秋。洛下章甫发重峰先生从祀之议。而以此乡为先生生长之地。搆送通草。要先通告于八路。以为将同声疏请之地。而生等妄意以先生节义道学。岂不允合于从祀。而第今既发之请。久未蒙 允。此时又发此论。则彼此妨碍。决无可成之理。姑徐徐以俟日后。观势而发之。亦未为晚。未知门下以为如何。此实斯文大议论。不可不一经勘定。故玆敢仰告伏乞商量下教。千万幸甚。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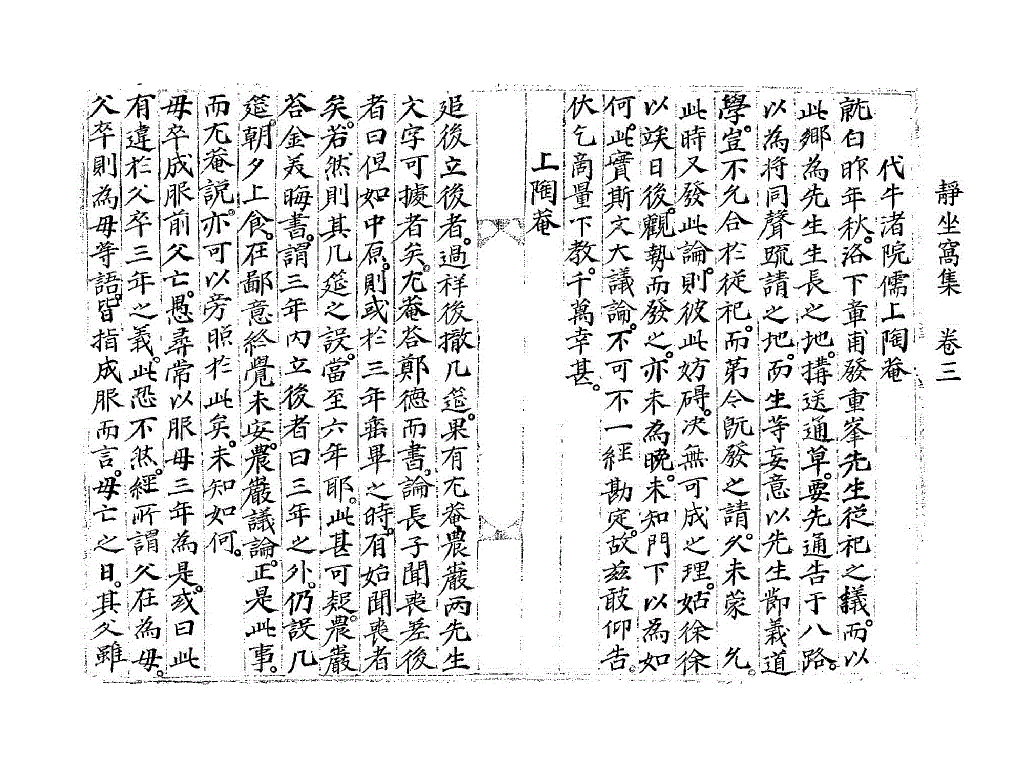 上陶庵
上陶庵追后立后者。过祥后撤几筵。果有尤庵,农岩两先生文字可据者矣。尤庵答郑德而书。论长子闻丧差后者曰但如中原。则或于三年垂毕之时。有始闻丧者矣。若然则其几筵之设。当至六年耶。此甚可疑。农岩答金美晦书。谓三年内立后者曰三年之外。仍设几筵。朝夕上食。在鄙意终觉未安。农岩议论。正是此事。而尤庵说。亦可以旁照于此矣。未知如何。
母卒成服前父亡。愚寻常以服母三年为是。或曰此有违于父卒三年之义。此恐不然。经所谓父在为母。父卒则为母等语。皆指成服而言。母亡之日。其父虽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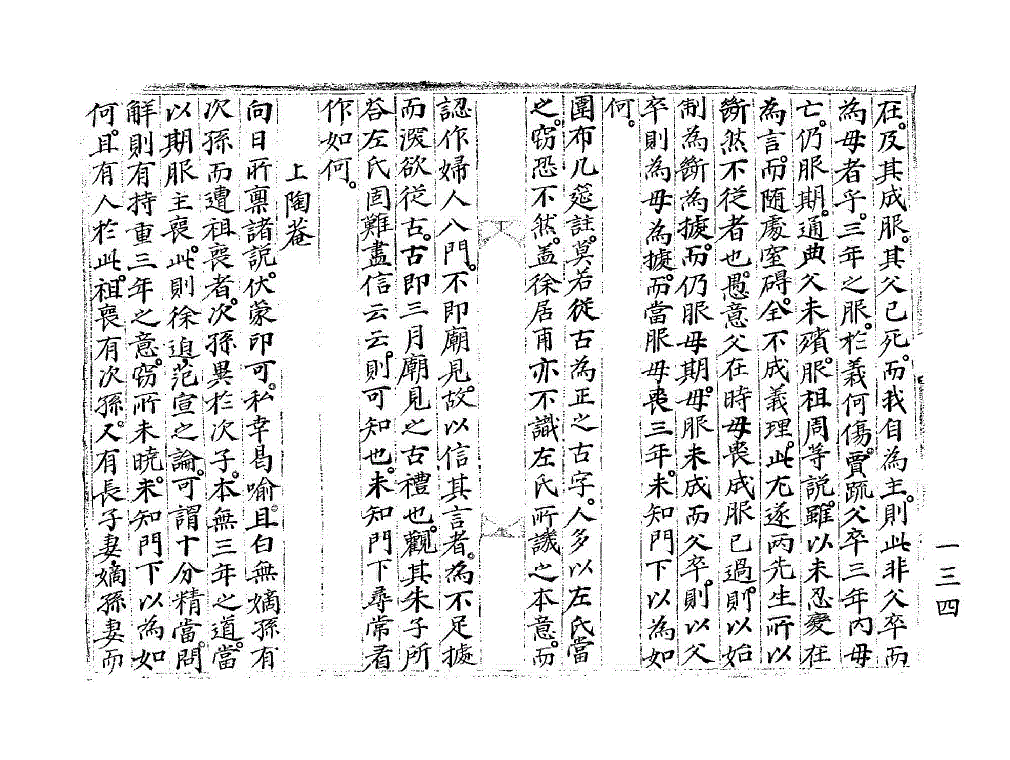 在。及其成服。其父已死。而我自为主。则此非父卒而为母者乎。三年之服。于义何伤。贾疏父卒三年内母亡。仍服期。通典父未殡。服祖周等说。虽以未忍变在为言。而随处窒碍。全不成义理。此尤遂两先生所以断然不从者也。愚意父在时母丧成服已过。则以始制为断为据。而仍服母期。母服未成而父卒。则以父卒则为母为据。而当服母丧三年。未知门下以为如何。
在。及其成服。其父已死。而我自为主。则此非父卒而为母者乎。三年之服。于义何伤。贾疏父卒三年内母亡。仍服期。通典父未殡。服祖周等说。虽以未忍变在为言。而随处窒碍。全不成义理。此尤遂两先生所以断然不从者也。愚意父在时母丧成服已过。则以始制为断为据。而仍服母期。母服未成而父卒。则以父卒则为母为据。而当服母丧三年。未知门下以为如何。围布几筵注。莫若从古为正之古字。人多以左氏当之。窃恐不然。盖徐居甫亦不识左氏所讥之本意。而认作妇人入门。不即庙见。故以信其言者。为不足据而深欲从古。古即三月庙见之古礼也。观其朱子所答左氏固难尽信云云。则可知也。未知门下寻常看作如何。
上陶庵
向日所禀诸说。伏蒙印可。私幸曷喻。且白无嫡孙有次孙而遭祖丧者。次孙异于次子。本无三年之道。当以期服主丧。此则徐𨓅,范宣之论。可谓十分精当。问解则有持重三年之意。窃所未晓。未知门下以为如何。且有人于此。祖丧有次孙。又有长子妻,嫡孙妻而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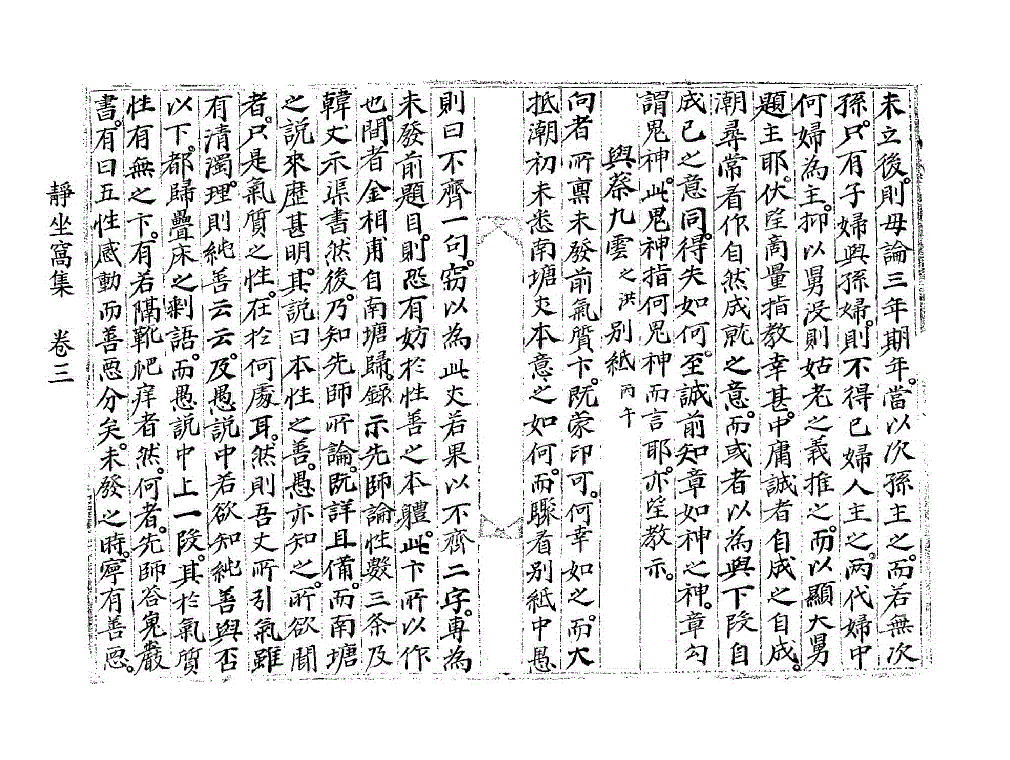 未立后。则毋论三年期年。当以次孙主之。而若无次孙。只有子妇与孙妇。则不得已妇人主之。两代妇中何妇为主。抑以舅没则姑老之义推之。而以显大舅题主耶。伏望商量指教幸甚。中庸诚者自成之自成。潮寻常看作自然成就之意。而或者以为与下段自成己之意同。得失如何。至诚前知章如神之神。章勾谓鬼神。此鬼神指何鬼神而言耶。亦望教示。
未立后。则毋论三年期年。当以次孙主之。而若无次孙。只有子妇与孙妇。则不得已妇人主之。两代妇中何妇为主。抑以舅没则姑老之义推之。而以显大舅题主耶。伏望商量指教幸甚。中庸诚者自成之自成。潮寻常看作自然成就之意。而或者以为与下段自成己之意同。得失如何。至诚前知章如神之神。章勾谓鬼神。此鬼神指何鬼神而言耶。亦望教示。与蔡九云(之洪)别纸(丙午)
向者所禀未发前气质卞。既蒙印可。何幸如之。而大抵潮初未悉南塘丈本意之如何。而骤看别纸中愚则曰不齐一句。窃以为此丈若果以不齐二字。专为未发前题目。则恐有妨于性善之本体。此卞所以作也。间者金相甫自南塘归。录示先师论性数三条及韩丈示渠书然后。乃知先师所论。既详且备。而南塘之说来历甚明。其说曰本性之善。愚亦知之。所欲闻者。只是气质之性。在于何处耳。然则吾丈所引气虽有清浊。理则纯善云云。及愚说中若欲知纯善与否以下。都归叠床之剩语。而愚说中上一段。其于气质性有无之卞。有若隔靴爬痒者然。何者。先师答嵬岩书。有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矣。未发之时。宁有善恶。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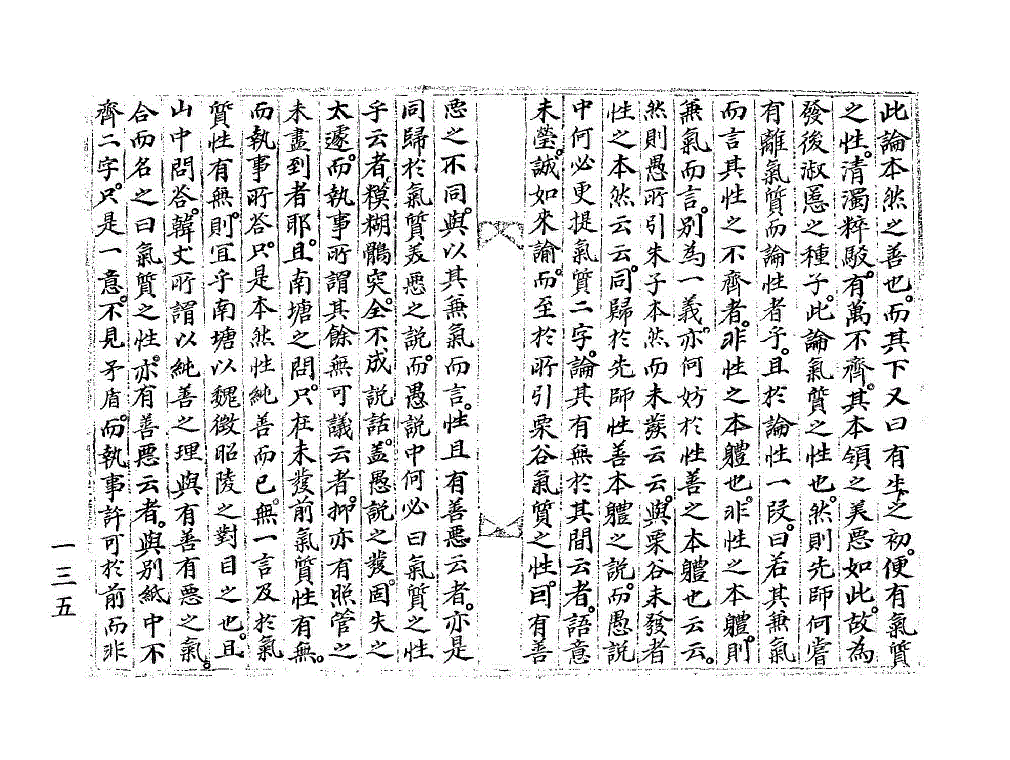 此论本然之善也。而其下又曰有生之初。便有气质之性。清浊粹驳。有万不齐。其本领之美恶如此。故为发后淑慝之种子。此论气质之性也。然则先师何尝有离气质而论性者乎。且于论性一段。曰若其兼气而言其性之不齐者。非性之本体也。非性之本体。则兼气而言。别为一义。亦何妨于性善之本体也云云。然则愚所引朱子本然而未发云云。与栗谷未发者性之本然云云。同归于先师性善本体之说。而愚说中何必更提气质二字。论其有无于其间云者。语意未莹。诚如来谕。而至于所引栗谷气质之性。因有善恶之不同。与以其兼气而言。性且有善恶云者。亦是同归于气质美恶之说。而愚说中何必曰气质之性乎云者。模糊鹘突。全不成说话。盖愚说之发。固失之太遽。而执事所谓其馀无可议云者。抑亦有照管之未尽到者耶。且南塘之问。只在未发前气质性有无。而执事所答。只是本然性纯善而已。无一言及于气质性有无。则宜乎南塘以魏徵昭陵之对目之也。且山中问答。韩丈所谓以纯善之理与有善有恶之气。合而名之曰气质之性。亦有善恶云者。与别纸中不齐二字。只是一意。不见矛盾。而执事许可于前而非
此论本然之善也。而其下又曰有生之初。便有气质之性。清浊粹驳。有万不齐。其本领之美恶如此。故为发后淑慝之种子。此论气质之性也。然则先师何尝有离气质而论性者乎。且于论性一段。曰若其兼气而言其性之不齐者。非性之本体也。非性之本体。则兼气而言。别为一义。亦何妨于性善之本体也云云。然则愚所引朱子本然而未发云云。与栗谷未发者性之本然云云。同归于先师性善本体之说。而愚说中何必更提气质二字。论其有无于其间云者。语意未莹。诚如来谕。而至于所引栗谷气质之性。因有善恶之不同。与以其兼气而言。性且有善恶云者。亦是同归于气质美恶之说。而愚说中何必曰气质之性乎云者。模糊鹘突。全不成说话。盖愚说之发。固失之太遽。而执事所谓其馀无可议云者。抑亦有照管之未尽到者耶。且南塘之问。只在未发前气质性有无。而执事所答。只是本然性纯善而已。无一言及于气质性有无。则宜乎南塘以魏徵昭陵之对目之也。且山中问答。韩丈所谓以纯善之理与有善有恶之气。合而名之曰气质之性。亦有善恶云者。与别纸中不齐二字。只是一意。不见矛盾。而执事许可于前而非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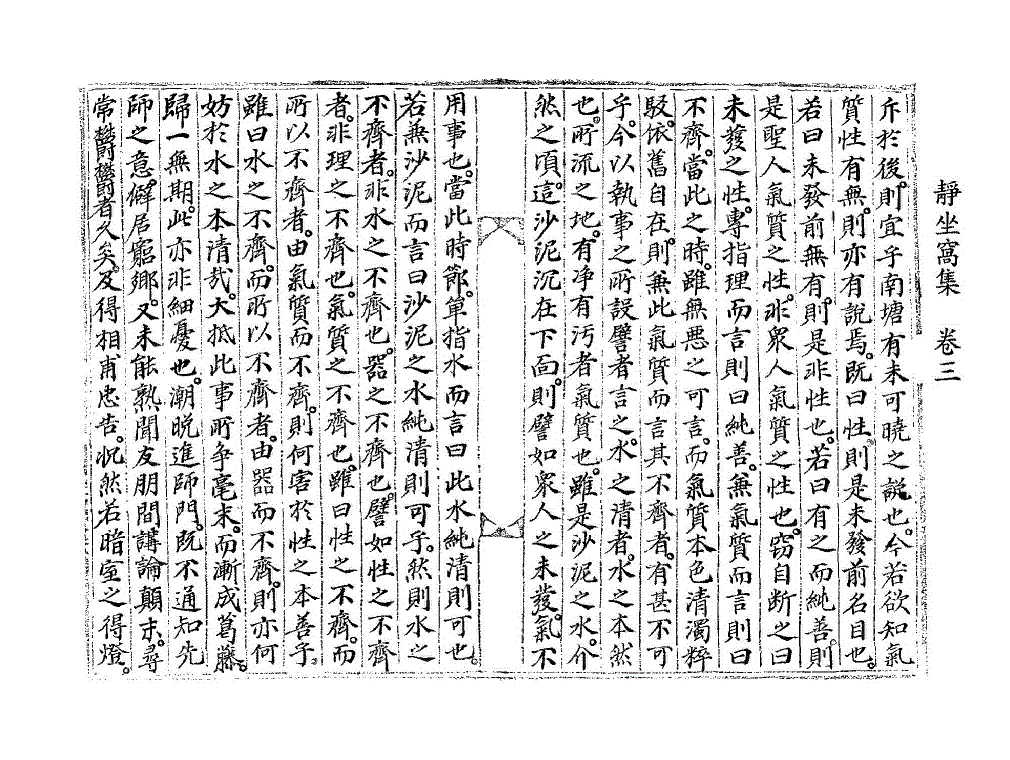 斥于后。则宜乎南塘有未可晓之说也。今若欲知气质性有无。则亦有说焉。既曰性。则是未发前名目也。若曰未发前无有。则是非性也。若曰有之而纯善。则是圣人气质之性。非众人气质之性也。窃自断之曰未发之性。专指理而言则曰纯善。兼气质而言则曰不齐。当此之时。虽无恶之可言。而气质本色清浊粹驳。依旧自在。则兼此气质而言其不齐者。有甚不可乎。今以执事之所设譬者言之。水之清者。水之本然也。所流之地。有净有污者气质也。虽是沙泥之水。介然之顷。这沙泥沉在下面。则譬如众人之未发。气不用事也。当此时节。单指水而言曰此水纯清则可也。若兼沙泥而言曰沙泥之水纯清则可乎。然则水之不齐者。非水之不齐也。器之不齐也。譬如性之不齐者。非理之不齐也。气质之不齐也。虽曰性之不齐。而所以不齐者。由气质而不齐。则何害于性之本善乎。虽曰水之不齐。而所以不齐者。由器而不齐。则亦何妨于水之本清哉。大抵此事所争毫末。而渐成葛藤。归一无期。此亦非细忧也。潮晚进师门。既不通知先师之意。僻居穷乡。又未能熟闻友朋间讲论颠末。寻常郁郁者久矣。及得相甫忠告。恍然若暗室之得灯。
斥于后。则宜乎南塘有未可晓之说也。今若欲知气质性有无。则亦有说焉。既曰性。则是未发前名目也。若曰未发前无有。则是非性也。若曰有之而纯善。则是圣人气质之性。非众人气质之性也。窃自断之曰未发之性。专指理而言则曰纯善。兼气质而言则曰不齐。当此之时。虽无恶之可言。而气质本色清浊粹驳。依旧自在。则兼此气质而言其不齐者。有甚不可乎。今以执事之所设譬者言之。水之清者。水之本然也。所流之地。有净有污者气质也。虽是沙泥之水。介然之顷。这沙泥沉在下面。则譬如众人之未发。气不用事也。当此时节。单指水而言曰此水纯清则可也。若兼沙泥而言曰沙泥之水纯清则可乎。然则水之不齐者。非水之不齐也。器之不齐也。譬如性之不齐者。非理之不齐也。气质之不齐也。虽曰性之不齐。而所以不齐者。由气质而不齐。则何害于性之本善乎。虽曰水之不齐。而所以不齐者。由器而不齐。则亦何妨于水之本清哉。大抵此事所争毫末。而渐成葛藤。归一无期。此亦非细忧也。潮晚进师门。既不通知先师之意。僻居穷乡。又未能熟闻友朋间讲论颠末。寻常郁郁者久矣。及得相甫忠告。恍然若暗室之得灯。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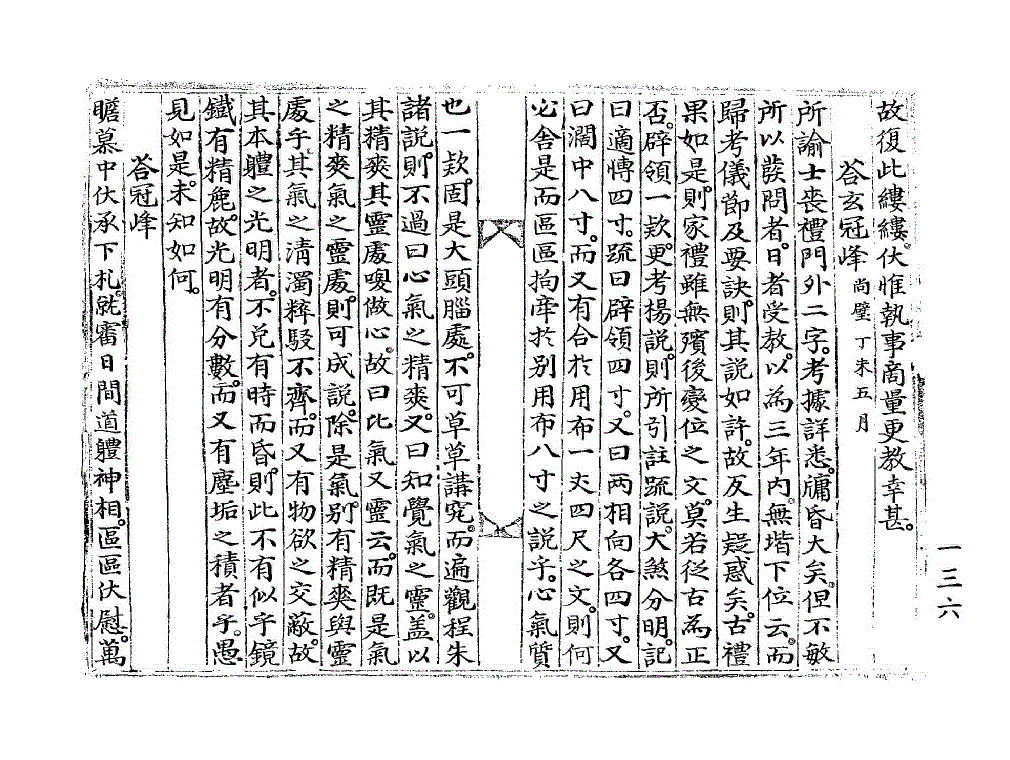 故复此缕缕。伏惟执事商量更教幸甚。
故复此缕缕。伏惟执事商量更教幸甚。答玄冠峰(尚璧○丁未五月)
所谕士丧礼门外二字。考据详悉。牖昏大矣。但不敏所以发问者。日者受教。以为三年内。无阶下位云。而归考仪节及要诀。则其说如许。故反生疑惑矣。古礼果如是。则家礼虽无殡后变位之文。莫若从古为正否。辟领一款。更考杨说。则所引注疏说。大煞分明。记曰适博四寸。疏曰辟领四寸。又曰两相向各四寸。又曰阔中八寸。而又有合于用布一丈四尺之文。则何必舍是而区区拘牵于别用布八寸之说乎。心气质也一款。固是大头脑处。不可草草讲究。而遍观程朱诸说。则不过曰心气之精爽。又曰知觉气之灵。盖以其精爽其灵处唤做心。故曰比气又灵云。而既是气之精爽气之灵处。则可成说。除是气。别有精爽与灵处乎。其气之清浊粹驳不齐。而又有物欲之交蔽。故其本体之光明者。不免有时而昏。则此不有似乎镜铁有精粗。故光明有分数。而又有尘垢之积者乎。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答冠峰
瞻慕中伏承下札。就审日间道体神相。区区伏慰。万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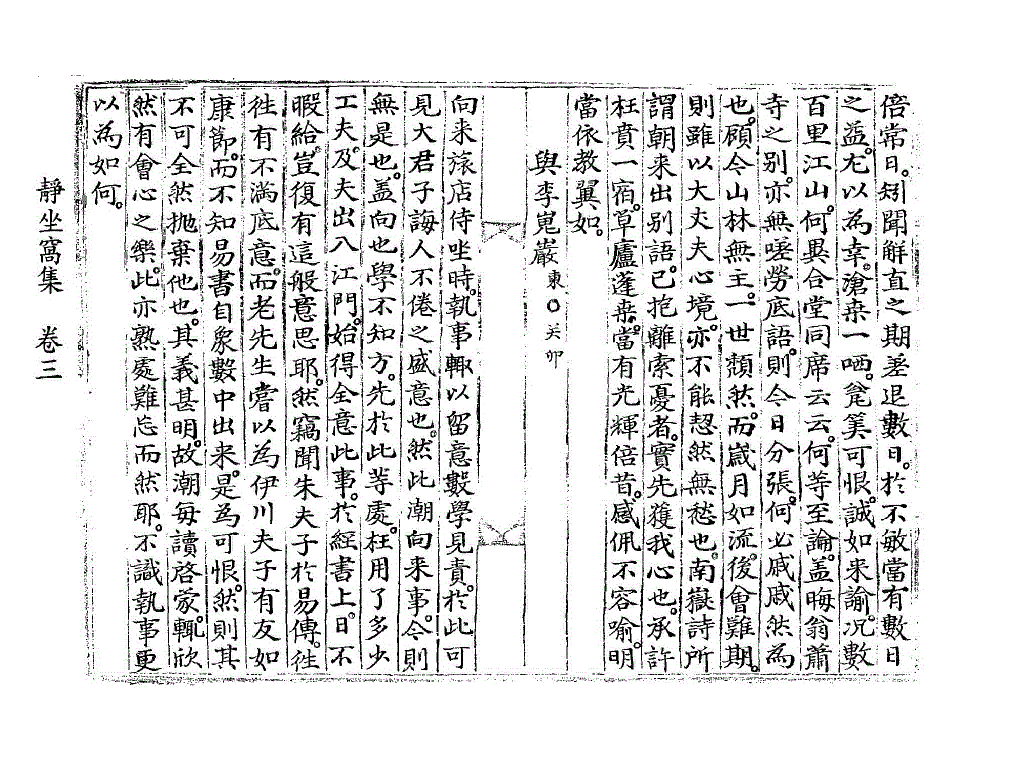 倍常日。矧闻解直之期差退数日。于不敏当有数日之益。尤以为幸。沧桑一哂。瓮算可恨。诚如来谕。况数百里江山。何异合堂同席云云。何等至论。盖晦翁萧寺之别。亦无嗟劳底语。则今日分张。何必戚戚然为也。顾今山林无主。一世颓然。而岁月如流。后会难期。则虽以大丈夫心境。亦不能恝然无愁也。南岳诗所谓朝来出别语。已抱离索忧者。实先获我心也。承许枉贲一宿。草庐蓬桑。当有光辉倍昔。感佩不容喻。明当依教翼如。
倍常日。矧闻解直之期差退数日。于不敏当有数日之益。尤以为幸。沧桑一哂。瓮算可恨。诚如来谕。况数百里江山。何异合堂同席云云。何等至论。盖晦翁萧寺之别。亦无嗟劳底语。则今日分张。何必戚戚然为也。顾今山林无主。一世颓然。而岁月如流。后会难期。则虽以大丈夫心境。亦不能恝然无愁也。南岳诗所谓朝来出别语。已抱离索忧者。实先获我心也。承许枉贲一宿。草庐蓬桑。当有光辉倍昔。感佩不容喻。明当依教翼如。与李嵬岩(柬○癸卯)
向来旅店侍坐时。执事辄以留意数学见责。于此可见大君子诲人不倦之盛意也。然此潮向来事。今则无是也。盖向也学不知方。先于此等处。枉用了多少工夫。及夫出入江门。始得全意此事。于经书上。日不暇给。岂复有这般意思耶。然窃闻朱夫子于易传。往往有不满底意。而老先生尝以为伊川夫子有友如康节。而不知易书自象数中出来。是为可恨。然则其不可全然抛弃他也。其义甚明。故潮每读启蒙。辄欣然有会心之乐。此亦熟处难忘而然耶。不识执事更以为如何。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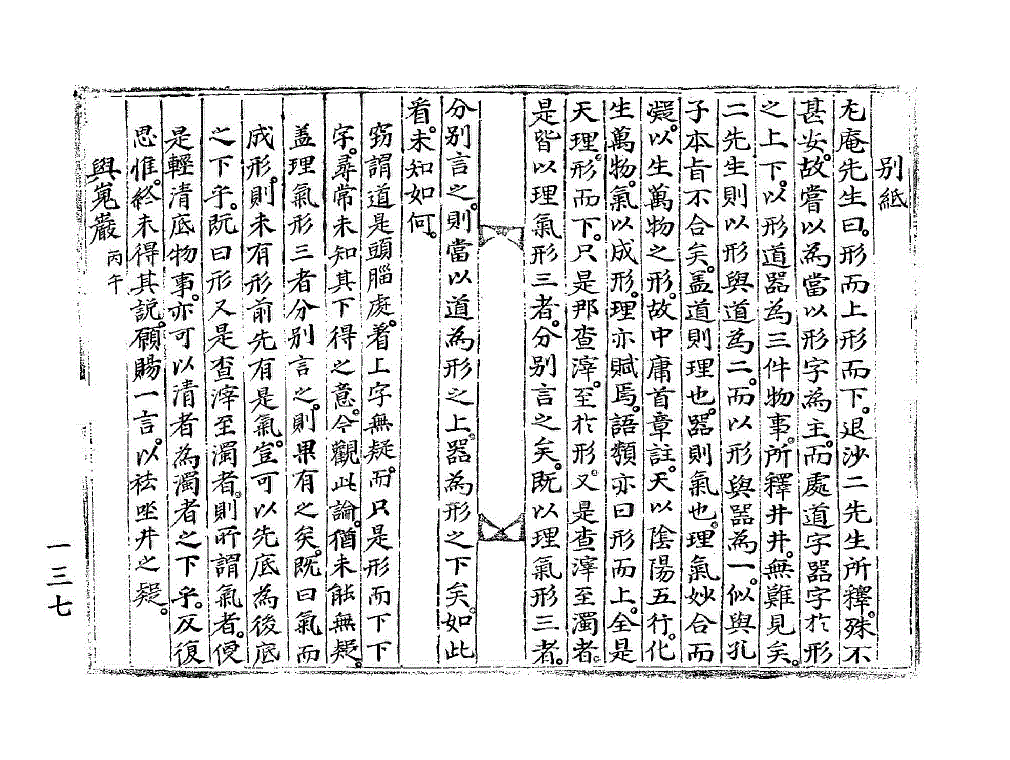 别纸
别纸尤庵先生曰。形而上形而下。退沙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尝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为三件物事。所释井井。无难见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以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语类亦曰形而上。全是天理。形而下。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浊者。是皆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矣。既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则当以道为形之上。器为形之下矣。如此看。未知如何。
窃谓道是头脑处。着上字无疑。而只是形而下下字。寻常未知其下得之意。今观此论。犹未能无疑。盖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则果有之矣。既曰气而成形。则未有形前先有是气。岂可以先底为后底之下乎。既曰形又是查滓至浊者。则所谓气者。便是轻清底物事。亦可以清者为浊者之下乎。反复思惟。终未得其说。愿赐一言。以祛坐井之疑。
与嵬岩(丙午)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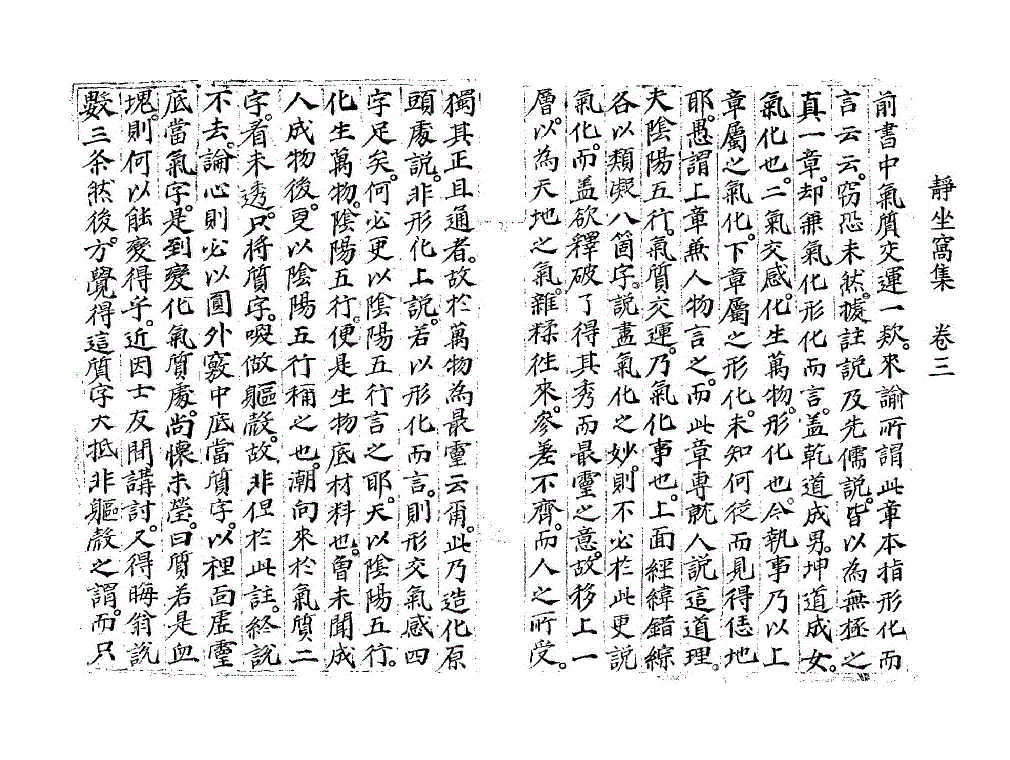 前书中气质交运一款。来谕所谓此章本指形化而言云云。窃恐未然。据注说及先儒说。皆以为无极之真一章。却兼气化形化而言。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气化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形化也。今执事乃以上章属之气化。下章属之形化。未知何从而见得恁地耶。愚谓上章兼人物言之。而此章专就人说这道理。夫阴阳五行。气质交运。乃气化事也。上面经纬错综各以类凝八个字。说尽气化之妙。则不必于此更说气化。而盖欲释破了得其秀而最灵之意。故移上一层。以为天地之气。杂糅往来。参差不齐。而人之所受。独其正且通者。故于万物为最灵云尔。此乃造化原头处说。非形化上说。若以形化而言。则形交气感四字足矣。何必更以阴阳五行言之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阴阳五行。便是生物底材料也。曾未闻成人成物后。更以阴阳五行称之也。潮向来于气质二字。看未透。只将质字。唤做躯壳。故非但于此注。终说不去。论心则必以圆外窍中底当质字。以里面虚灵底当气字。是到变化气质处。尚怀未莹。曰质若是血块。则何以能变得乎。近因士友间讲讨。又得晦翁说数三条然后。方觉得这质字大抵非躯壳之谓。而只
前书中气质交运一款。来谕所谓此章本指形化而言云云。窃恐未然。据注说及先儒说。皆以为无极之真一章。却兼气化形化而言。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气化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形化也。今执事乃以上章属之气化。下章属之形化。未知何从而见得恁地耶。愚谓上章兼人物言之。而此章专就人说这道理。夫阴阳五行。气质交运。乃气化事也。上面经纬错综各以类凝八个字。说尽气化之妙。则不必于此更说气化。而盖欲释破了得其秀而最灵之意。故移上一层。以为天地之气。杂糅往来。参差不齐。而人之所受。独其正且通者。故于万物为最灵云尔。此乃造化原头处说。非形化上说。若以形化而言。则形交气感四字足矣。何必更以阴阳五行言之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阴阳五行。便是生物底材料也。曾未闻成人成物后。更以阴阳五行称之也。潮向来于气质二字。看未透。只将质字。唤做躯壳。故非但于此注。终说不去。论心则必以圆外窍中底当质字。以里面虚灵底当气字。是到变化气质处。尚怀未莹。曰质若是血块。则何以能变得乎。近因士友间讲讨。又得晦翁说数三条然后。方觉得这质字大抵非躯壳之谓。而只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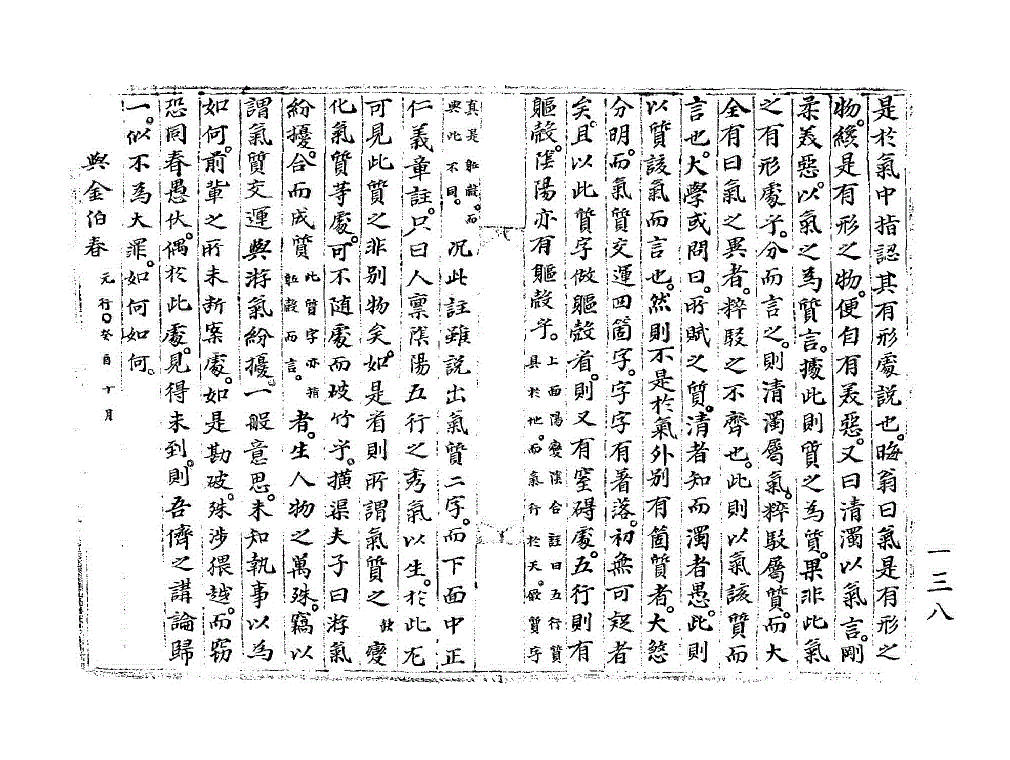 是于气中指认其有形处说也。晦翁曰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恶。又曰清浊以气言。刚柔美恶。以气之为质言。据此则质之为质。果非此气之有形处乎。分而言之。则清浊属气。粹驳属质。而大全有曰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也。此则以气该质而言也。大学或问曰。所赋之质。清者知而浊者愚。此则以质该气而言也。然则不是于气外别有个质者。大煞分明。而气质交运四个字。字字有着落。初无可疑者矣。且以此质字做躯壳看。则又有窒碍处。五行则有躯壳。阴阳亦有躯壳乎。(上面阳变阴合注曰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厥质字真是𨈬壳。而与此不同。)况此注虽说出气质二字。而下面中正仁义章注。只曰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于此尤可见此质之非别物矣。如是看则所谓气质之(缺)变化气质等处。可不随处而破竹乎。横渠夫子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此质字亦指𨈬壳而言。)者。生人物之万殊。窃以谓气质交运与游气纷扰。一般意思。未知执事以为如何。前辈之所未断案处。如是勘破。殊涉猥越。而窃恐同春,愚伏。偶于此处。见得未到。则吾侪之讲论归一。似不为大罪。如何如何。
是于气中指认其有形处说也。晦翁曰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恶。又曰清浊以气言。刚柔美恶。以气之为质言。据此则质之为质。果非此气之有形处乎。分而言之。则清浊属气。粹驳属质。而大全有曰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也。此则以气该质而言也。大学或问曰。所赋之质。清者知而浊者愚。此则以质该气而言也。然则不是于气外别有个质者。大煞分明。而气质交运四个字。字字有着落。初无可疑者矣。且以此质字做躯壳看。则又有窒碍处。五行则有躯壳。阴阳亦有躯壳乎。(上面阳变阴合注曰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厥质字真是𨈬壳。而与此不同。)况此注虽说出气质二字。而下面中正仁义章注。只曰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于此尤可见此质之非别物矣。如是看则所谓气质之(缺)变化气质等处。可不随处而破竹乎。横渠夫子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此质字亦指𨈬壳而言。)者。生人物之万殊。窃以谓气质交运与游气纷扰。一般意思。未知执事以为如何。前辈之所未断案处。如是勘破。殊涉猥越。而窃恐同春,愚伏。偶于此处。见得未到。则吾侪之讲论归一。似不为大罪。如何如何。与金伯春(元行○癸酉十月)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9H 页
 赠玄纁一节。归考尤翁礼说。则答李汝九族孙三锡李厦卿三书。皆以柩旁看作棺椁之间。不啻明白矣。乡谷无仪礼。执事柩上之證。姑未知如何。而无乃出于疏说而不足据耶。若经传所载。可以为法。则尤翁何以曰柩上之说无据。以南溪考据该博。而亦曰置玄纁于柩上。恐无义乎。幸更教之。
赠玄纁一节。归考尤翁礼说。则答李汝九族孙三锡李厦卿三书。皆以柩旁看作棺椁之间。不啻明白矣。乡谷无仪礼。执事柩上之證。姑未知如何。而无乃出于疏说而不足据耶。若经传所载。可以为法。则尤翁何以曰柩上之说无据。以南溪考据该博。而亦曰置玄纁于柩上。恐无义乎。幸更教之。与金伯春(甲戌六月)
赠玄纁一款。厥后得仪礼一书。细考上下文义。始知高明之论。果有据依矣。盖实币于盖。疏既有载而之圹之文。窆条只曰赠玄纁。而不言置处。则安知非蒙上文而置柩之上面耶。然既不能明知其本意。则千载之下。有难质言。家礼则曰置于柩旁。柩旁明是棺椁之间。而只曰柩旁。不言柩之某旁。则是亦不能无惑也。沙溪引开元礼以上玄下纁为言。而开元礼柩东若出于左服则左服。即南首时授右之义。而不可施于北首。此虽礼家承用之久。而既知无义。不可强从。尤翁之右玄左纁。则虽无古据。而分置左右。不害为柩旁。以西为上。又不失上玄而下纁。愚意自今为始。窃欲以此为正。未知兄意又以为如何。
答金伯春(六月)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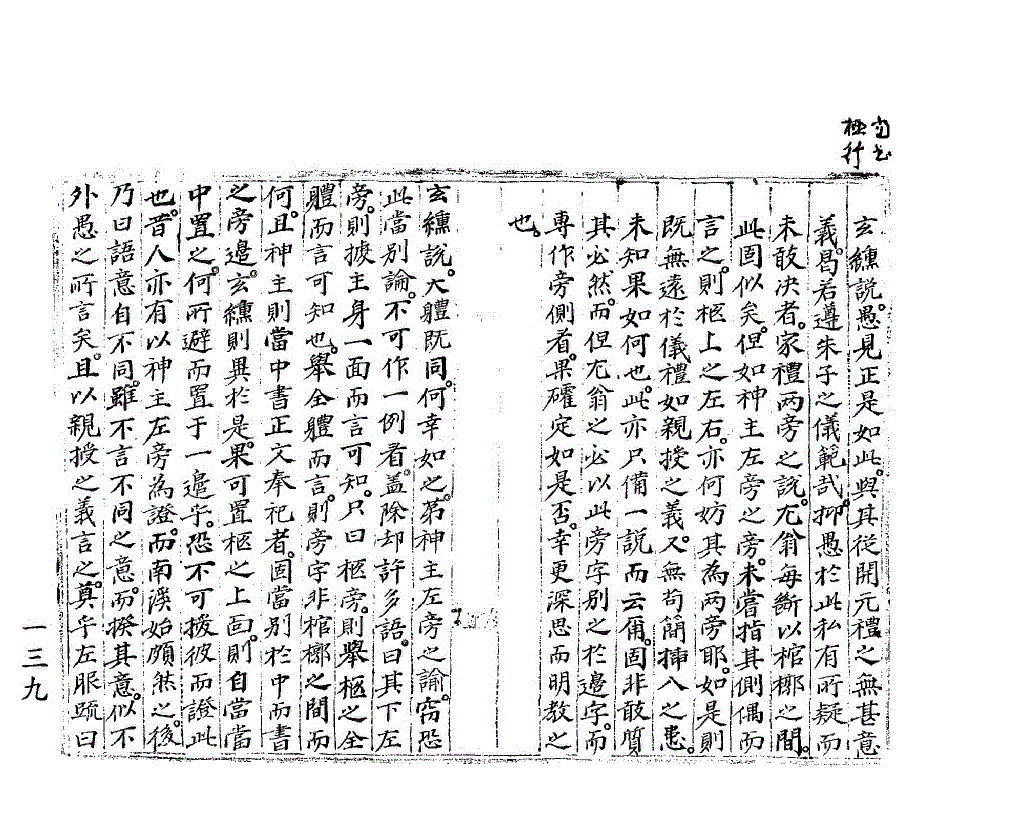 주-D001玄纁说。愚见正是如此。与其从开元礼之无甚意义。曷若遵朱子之仪范哉。抑愚于此私有所疑而未敢决者。家礼两旁之说。尤翁每断以棺椁之间。此固似矣。但如神主左旁之旁。未尝指其侧偶而言之。则柩上之左右。亦何妨其为两旁耶。如是则既无远于仪礼如亲授之义。又无苟简插入之患。未知果如何也。此亦只备一说而云尔。固非敢质其必然。而但尤翁之必以此旁字别之于边字。而专作旁侧看。果礭定如是否。幸更深思而明教之也。
주-D001玄纁说。愚见正是如此。与其从开元礼之无甚意义。曷若遵朱子之仪范哉。抑愚于此私有所疑而未敢决者。家礼两旁之说。尤翁每断以棺椁之间。此固似矣。但如神主左旁之旁。未尝指其侧偶而言之。则柩上之左右。亦何妨其为两旁耶。如是则既无远于仪礼如亲授之义。又无苟简插入之患。未知果如何也。此亦只备一说而云尔。固非敢质其必然。而但尤翁之必以此旁字别之于边字。而专作旁侧看。果礭定如是否。幸更深思而明教之也。玄纁说。大体既同。何幸如之。第神主左旁之谕。窃恐此当别论。不可作一例看。盖除却许多语。曰其下左旁。则据主身一面而言可知。只曰柩旁。则举柩之全体而言可知也。举全体而言。则旁字非棺椁之间而何。且神主则当中书正文奉祀者。固当别于中而书之旁边。玄纁则异于是。果可置柩之上面。则自当当中置之。何所避而置于一边乎。恐不可援彼而證此也。昔人亦有以神主左旁为證。而南溪始颇然之。后乃曰语意自不同。虽不言不同之意。而揆其意。似不外愚之所言矣。且以亲授之义言之。奠乎左服疏曰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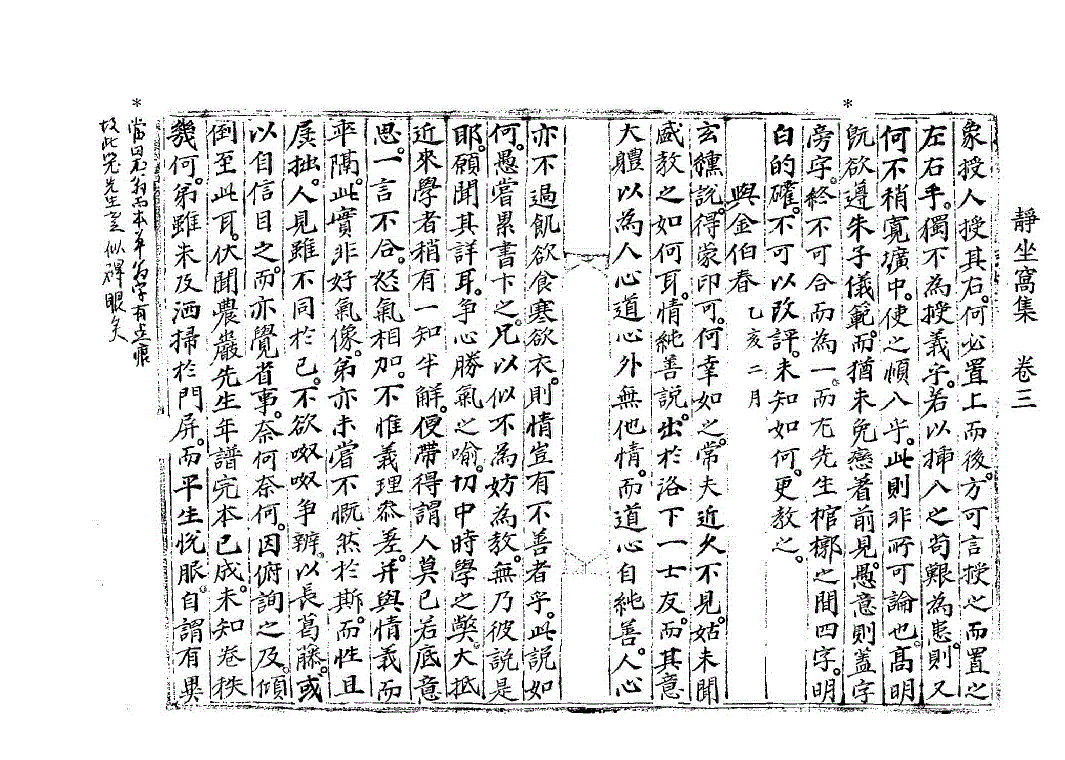 象授人授其右。何必置上而后。方可言授之而置之左右手。独不为授义乎。若以插入之苟艰为患。则又何不稍宽圹中。使之㥧入乎。此则非所可论也。高明既欲遵朱子仪范。而犹未免恋着前见。愚意则盖字旁字。终不可合而为一。而尤先生(当曰尤翁。而本草翁字。有点痕。故此以尤先生书之。似碍眼矣。)棺椁之间四字。明白的礭。不可以改评。未知如何。更教之。
象授人授其右。何必置上而后。方可言授之而置之左右手。独不为授义乎。若以插入之苟艰为患。则又何不稍宽圹中。使之㥧入乎。此则非所可论也。高明既欲遵朱子仪范。而犹未免恋着前见。愚意则盖字旁字。终不可合而为一。而尤先生(当曰尤翁。而本草翁字。有点痕。故此以尤先生书之。似碍眼矣。)棺椁之间四字。明白的礭。不可以改评。未知如何。更教之。与金伯春(乙亥二月)
玄纁说。得蒙印可。何幸如之。常夫近久不见。姑未闻盛教之如何耳。情纯善说。出于洛下一士友。而其意大体以为人心道心外无他情。而道心自纯善。人心亦不过饥欲食寒欲衣。则情岂有不善者乎。此说如何。愚尝累书卞之。兄以似不为妨为教。无乃彼说是耶。愿闻其详耳。争心胜气之喻。切中时学之弊。大抵近来学者稍有一知半解。便带得谓人莫己若底意思。一言不合。怒气相加。不惟义理参差。并与情义而乖隔。此实非好气像。弟亦未尝不慨然于斯。而性且孱拙。人见虽不同于己。不欲呶呶争辨。以长葛藤。或以自信目之。而亦觉省事。奈何奈何。因俯询之及。倾倒至此耳。伏闻农岩先生年谱完本已成。未知卷秩几何。弟虽未及洒扫于门屏。而平生悦服。自谓有异
静坐窝先生集卷之三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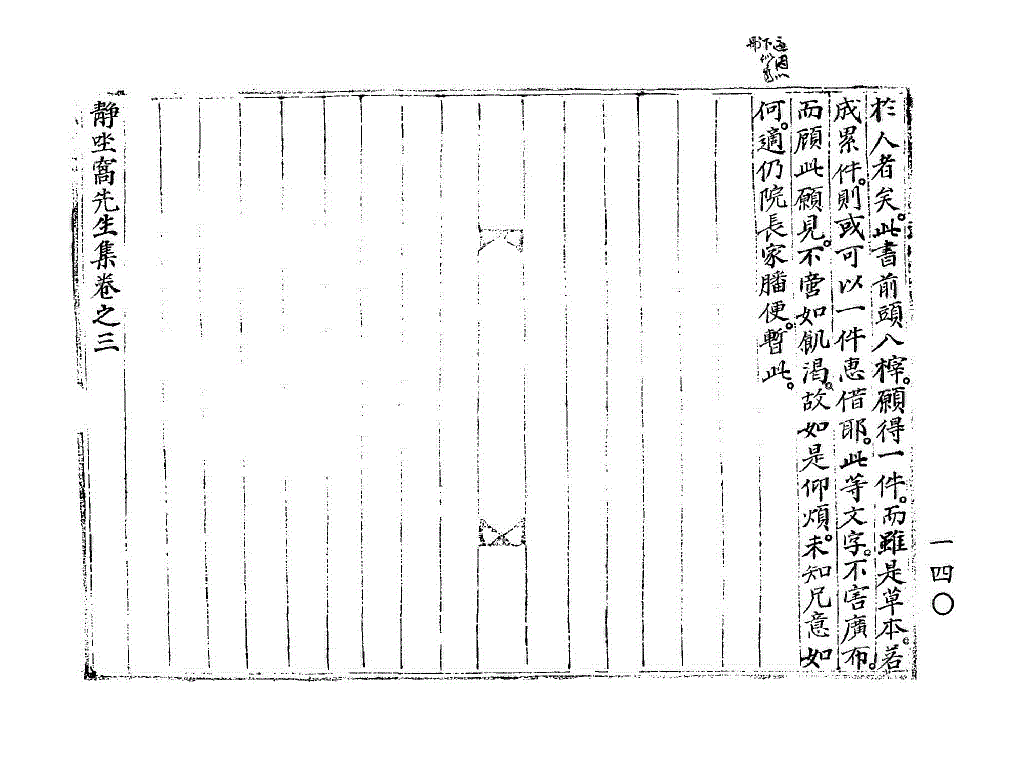 于人者矣。此书前头入梓。愿得一件。而虽是草本。若成累件。则或可以一件惠借耶。此等文字。不害广布。而顾此愿见。不啻如饥渴。故如是仰烦。未知兄意如何。适(适因以下。似当删。)仍院长家膰便。暂此。
于人者矣。此书前头入梓。愿得一件。而虽是草本。若成累件。则或可以一件惠借耶。此等文字。不害广布。而顾此愿见。不啻如饥渴。故如是仰烦。未知兄意如何。适(适因以下。似当删。)仍院长家膰便。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