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沙村集卷之四 第 x 页
沙村集卷之四
策
策
沙村集卷之四 第 317H 页
 [儒老佛]
[儒老佛]问。吾儒及老佛。号称三教。而中古以降。高明俊才之士。出于此则入乎彼。先贤至以为弥近理而大乱真。择术求道者。不可不辨之早察之精也。儒者曰。太极生两仪。老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其说出源头。既甚相近。儒者之尽性。老氏之载魄。佛氏之见心。其用心于内者。亦不悬殊。曰一以贯之。曰圣人抱一。曰万法归一。其守约之旨则无异。曰修己以安百姓。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曰慈悲以度众生。其济物之心则略同。凡此数条。同中之异。似是而非者。皆可历举而明辨耶。邵子称老氏得易之体。伊川称庄子形容道体尽好。文中子谓佛为圣人。和靖谓观音为贤者。以诸公道学之正。而反有所称许何也。上蔡亲炙程门。而淫于老佛。象山动引孟子。而近于禅旨。以平生论辨之正。而终不免浸染者。何欤。张子房纯用黄老。而南轩谓有儒者气像。苏子瞻到处参禅。而晦翁谓以近世名卿。两贤之严于排辟。而
沙村集卷之四 第 317L 页
 评品若此者。何欤。我 朝前辈。亦尝有出入泛滥者矣。挽近以来。绝不闻有说及空有论极玄虚之士。若以为吾道大行。士无异议而然也。则宜其真儒蔚兴。圣学复明。而殆亦有不然者。何欤。何以则于近理而乱真者。剖析无遗。使择术求道者。无他歧之惑。而三教之异同。会归于一道之正耶。诸生讲学有素。必能研穷于心性精微之蕴。道术源流之辨。无以科场例套自拘。妙论而详说之。
评品若此者。何欤。我 朝前辈。亦尝有出入泛滥者矣。挽近以来。绝不闻有说及空有论极玄虚之士。若以为吾道大行。士无异议而然也。则宜其真儒蔚兴。圣学复明。而殆亦有不然者。何欤。何以则于近理而乱真者。剖析无遗。使择术求道者。无他歧之惑。而三教之异同。会归于一道之正耶。诸生讲学有素。必能研穷于心性精微之蕴。道术源流之辨。无以科场例套自拘。妙论而详说之。对。呜呼。圣人既殁而邪说行。真儒不作而异端起。曰老曰佛。与吾儒鼎峙。相为升降。互有消长。而其为教也。尽有一二依俙彷佛于儒者之道。迷人眼目。眩人心志。如越佗之黄屋左纛。而人不觉其僭伪之贼。则有能于此。距诐放淫。声罪致讨。以成其内修外攘之烈者乎。汉唐以来。所谓儒者。不过规规于章句之末。训诂之间耳。没身从事。当面差过。性命之学。不曾梦到。使此个田地。荒芜百载。而被他二氏之割据盗占。则尚安能窥其藩篱而发其情状乎。间虽有自任以排辟者。而于三教之同异是非。率皆落在浅处。但执粗迹。其所龃龉模糊之说。适为隔靴爬痒之归矣。若
沙村集卷之四 第 318H 页
 其心术隐微之处。本末疑似之间。则不能明捉真赃的投对剂。杯水莫救于车薪。寸胶无补于浊河。彼不但不服也。方且日新月盛。流毒肆害而无所忌惮。世道之忧。有不可胜言。向非洛闽诸夫子出。阐明儒教。钩摘潜慝。照烛于伯阳之稗道。燃犀于释门之伪法。一刀两断。拔本塞源。则其不率天下而归二氏者。几希矣。今执事忧儒术之不振。虑异教之误人。发策试士。特询三教。思闻诸生之辨论。欲见学识之醇疵。噫嘻意甚盛也。真所谓能言距杨墨而圣人之徒也。儱侗末学。虽不敢容易臆对。而第得于洛闽之绪言者则有之。敢不搜集旧闻。悉心仰复乎。窃谓世有三教。儒也老也佛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儒之教也。玄虚为务。清净是尚者。老之教也。空幻驾说。寂灭立法者。佛之教也。派分源别。并行于世。而中古以来。老佛二教最盛。聪明之人。才智之士。率未免浸淫其教。渐染其学。才出乎此。必入于彼。盖三教之辨。虽自有邪正之判。而若其所争之端。则仅隔一发耳。其立言之间。诚有所赜微臻妙。而与吾儒相似者矣。其下工之际。诚有所穷奥造蕴。而与吾儒相近者矣。其设教诲人之道。又却切近逼拶。而与吾儒相左者。亦无几矣。
其心术隐微之处。本末疑似之间。则不能明捉真赃的投对剂。杯水莫救于车薪。寸胶无补于浊河。彼不但不服也。方且日新月盛。流毒肆害而无所忌惮。世道之忧。有不可胜言。向非洛闽诸夫子出。阐明儒教。钩摘潜慝。照烛于伯阳之稗道。燃犀于释门之伪法。一刀两断。拔本塞源。则其不率天下而归二氏者。几希矣。今执事忧儒术之不振。虑异教之误人。发策试士。特询三教。思闻诸生之辨论。欲见学识之醇疵。噫嘻意甚盛也。真所谓能言距杨墨而圣人之徒也。儱侗末学。虽不敢容易臆对。而第得于洛闽之绪言者则有之。敢不搜集旧闻。悉心仰复乎。窃谓世有三教。儒也老也佛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儒之教也。玄虚为务。清净是尚者。老之教也。空幻驾说。寂灭立法者。佛之教也。派分源别。并行于世。而中古以来。老佛二教最盛。聪明之人。才智之士。率未免浸淫其教。渐染其学。才出乎此。必入于彼。盖三教之辨。虽自有邪正之判。而若其所争之端。则仅隔一发耳。其立言之间。诚有所赜微臻妙。而与吾儒相似者矣。其下工之际。诚有所穷奥造蕴。而与吾儒相近者矣。其设教诲人之道。又却切近逼拶。而与吾儒相左者。亦无几矣。沙村集卷之四 第 318L 页
 莠苗相混而难分其真赝也。朱紫相错而难别其主客也。其说愈工而吾儒之害愈大。其教益精而吾儒之祸益深。后学所以相率归之。靡然从之者。莫非此也。而先儒所谓弥近理大乱真者。有见乎是夫。是以学者。于吾儒及二家之教。辨之不早。则无以洞观于同异之原。察之不精。则无以明觑乎。是非之迹。始或少忽。则其终也冥行于玄牝之圈套矣。初若一误。则其后也擿埴于葱岭之世界矣。毫釐有差而必致千里之谬。涓流不塞而必有滔天之患。由是而榛芜于圣路。由是而螮蝀于斯道。坠坑落堑。漫不知悟而毕竟至于糠秕仁义。泡幻伦常。斁天理灭人纪而后已。择术求道者。其可不审慎于此哉。虽然。阳盛则阴衰。正胜则邪熄。苟使孔孟相传之道。程朱所讲之学。复明于斯世。大行于今日。如日月中天。昭晢呈露。则彼老佛者。手脚破绽。情迹莫逃。喧豗之言。阴沴之气。举将点雪于洪炉矣。然则学者何修而可致此也。其尊德性道问学之谓乎。请因明问而究三教之辨焉。呜呼。所谓太极生两仪者。吾儒之言也。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老氏之论也。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者。佛者之说也。其源头说出者。可谓相近矣。然
莠苗相混而难分其真赝也。朱紫相错而难别其主客也。其说愈工而吾儒之害愈大。其教益精而吾儒之祸益深。后学所以相率归之。靡然从之者。莫非此也。而先儒所谓弥近理大乱真者。有见乎是夫。是以学者。于吾儒及二家之教。辨之不早。则无以洞观于同异之原。察之不精。则无以明觑乎。是非之迹。始或少忽。则其终也冥行于玄牝之圈套矣。初若一误。则其后也擿埴于葱岭之世界矣。毫釐有差而必致千里之谬。涓流不塞而必有滔天之患。由是而榛芜于圣路。由是而螮蝀于斯道。坠坑落堑。漫不知悟而毕竟至于糠秕仁义。泡幻伦常。斁天理灭人纪而后已。择术求道者。其可不审慎于此哉。虽然。阳盛则阴衰。正胜则邪熄。苟使孔孟相传之道。程朱所讲之学。复明于斯世。大行于今日。如日月中天。昭晢呈露。则彼老佛者。手脚破绽。情迹莫逃。喧豗之言。阴沴之气。举将点雪于洪炉矣。然则学者何修而可致此也。其尊德性道问学之谓乎。请因明问而究三教之辨焉。呜呼。所谓太极生两仪者。吾儒之言也。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老氏之论也。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者。佛者之说也。其源头说出者。可谓相近矣。然沙村集卷之四 第 319H 页
 而吾儒之为此说也。必以一而字著于无极太极之间。其所以动生阳静生阴。生四象生八卦者。分明说得。而兼管动静。统言理气。煞有次第。煞有本末。此吾儒所以卓见大本之原。究极精微之域者。朱夫子与陆子静。辨之详矣。而老氏之说。则尽有疑焉。既曰混成则是有形之物也。又曰。先天地生则是无形之物也。混成二字。气已成形之时也。先天地三字。气未用事之时也。一句间旨意。自相矛盾者如此。况其下有贵玄牝之语。则其遗弃事物之意已萌矣。其视吾儒所谓无极而太极。动生阳静生阴之言。同乎异乎。佛者之论。则又有可异者。其曰先天地无形寂寥者。只言无极而不言太极也。只言静处而不言动处也。况中间遮隔许多层级。拔脱许多次第。没却化化生生之理。而突然插著祖万物之语。若是则无形寂寥者。为悬空独立之物。而无所依倚。无所著落。其为万物之祖者。未免于偏枯不仁。而其空灭事物之意已现矣。其视吾儒所谓二五之精。无极之真。氤氲妙合。生物生人者。是乎非乎。呜呼。吾儒以尽性为学。老氏以载魄为道。佛者以见心为法。其用心于内者。似不悬殊也。然而吾儒之为学也。必先穷理格物。以尽夫所
而吾儒之为此说也。必以一而字著于无极太极之间。其所以动生阳静生阴。生四象生八卦者。分明说得。而兼管动静。统言理气。煞有次第。煞有本末。此吾儒所以卓见大本之原。究极精微之域者。朱夫子与陆子静。辨之详矣。而老氏之说。则尽有疑焉。既曰混成则是有形之物也。又曰。先天地生则是无形之物也。混成二字。气已成形之时也。先天地三字。气未用事之时也。一句间旨意。自相矛盾者如此。况其下有贵玄牝之语。则其遗弃事物之意已萌矣。其视吾儒所谓无极而太极。动生阳静生阴之言。同乎异乎。佛者之论。则又有可异者。其曰先天地无形寂寥者。只言无极而不言太极也。只言静处而不言动处也。况中间遮隔许多层级。拔脱许多次第。没却化化生生之理。而突然插著祖万物之语。若是则无形寂寥者。为悬空独立之物。而无所依倚。无所著落。其为万物之祖者。未免于偏枯不仁。而其空灭事物之意已现矣。其视吾儒所谓二五之精。无极之真。氤氲妙合。生物生人者。是乎非乎。呜呼。吾儒以尽性为学。老氏以载魄为道。佛者以见心为法。其用心于内者。似不悬殊也。然而吾儒之为学也。必先穷理格物。以尽夫所沙村集卷之四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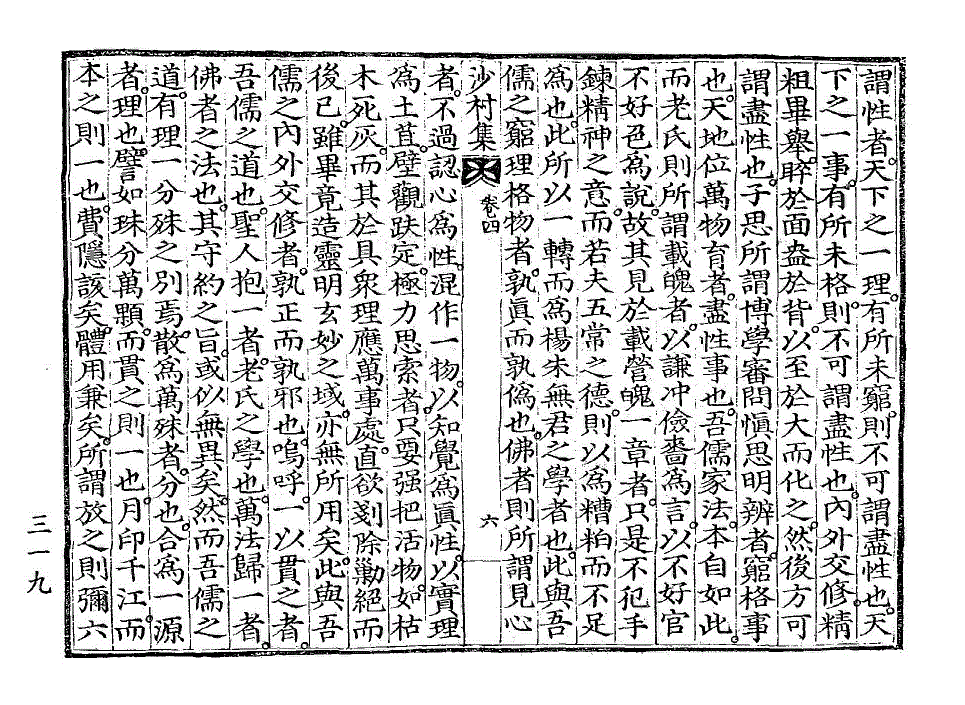 谓性者。天下之一理。有所未穷。则不可谓尽性也。天下之一事。有所未格。则不可谓尽性也。内外交修。精粗毕举。睟于面盎于背。以至于大而化之。然后方可谓尽性也。子思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者。穷格事也。天地位万物育者。尽性事也。吾儒家法。本自如此。而老氏则所谓载魄者。以谦冲俭啬为言。以不好官不好色为说。故其见于载营魄一章者。只是不犯手鍊精神之意。而若夫五常之德。则以为糟粕而不足为也。此所以一转而为杨朱无君之学者也。此与吾儒之穷理格物者。孰真而孰伪也。佛者则所谓见心者。不过认心为性。混作一物。以知觉为真性。以实理为土苴。壁观趺定。极力思索者。只要强把活物。如枯木死灰。而其于具众理应万事处。直欲刬除剿绝而后已。虽毕竟造灵明玄妙之域。亦无所用矣。此与吾儒之内外交修者。孰正而孰邪也。呜呼。一以贯之者。吾儒之道也。圣人抱一者。老氏之学也。万法归一者。佛者之法也。其守约之旨。或似无异矣。然而吾儒之道。有理一分殊之别焉。散为万殊者。分也。合为一源者。理也。譬如珠分万颗。而贯之则一也。月印千江。而本之则一也。费隐该矣。体用兼矣。所谓放之则弥六
谓性者。天下之一理。有所未穷。则不可谓尽性也。天下之一事。有所未格。则不可谓尽性也。内外交修。精粗毕举。睟于面盎于背。以至于大而化之。然后方可谓尽性也。子思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者。穷格事也。天地位万物育者。尽性事也。吾儒家法。本自如此。而老氏则所谓载魄者。以谦冲俭啬为言。以不好官不好色为说。故其见于载营魄一章者。只是不犯手鍊精神之意。而若夫五常之德。则以为糟粕而不足为也。此所以一转而为杨朱无君之学者也。此与吾儒之穷理格物者。孰真而孰伪也。佛者则所谓见心者。不过认心为性。混作一物。以知觉为真性。以实理为土苴。壁观趺定。极力思索者。只要强把活物。如枯木死灰。而其于具众理应万事处。直欲刬除剿绝而后已。虽毕竟造灵明玄妙之域。亦无所用矣。此与吾儒之内外交修者。孰正而孰邪也。呜呼。一以贯之者。吾儒之道也。圣人抱一者。老氏之学也。万法归一者。佛者之法也。其守约之旨。或似无异矣。然而吾儒之道。有理一分殊之别焉。散为万殊者。分也。合为一源者。理也。譬如珠分万颗。而贯之则一也。月印千江。而本之则一也。费隐该矣。体用兼矣。所谓放之则弥六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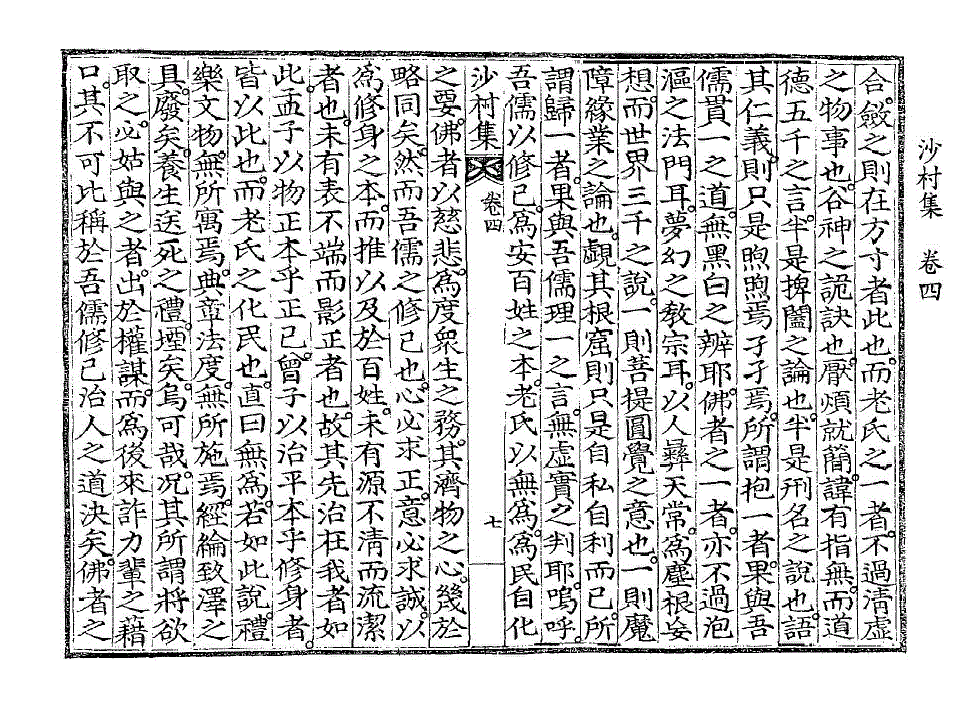 合。敛之则在方寸者此也。而老氏之一者。不过清虚之物事也。谷神之诡诀也。厌烦就简。讳有指无。而道德五千之言。半是捭阖之论也。半是刑名之说也。语其仁义。则只是煦煦焉孑孑焉。所谓抱一者。果与吾儒贯一之道。无黑白之辨耶。佛者之一者。亦不过泡沤之法门耳。梦幻之教宗耳。以人彝天常。为尘根妄想。而世界三千之说。一则菩提圆觉之意也。一则魔障缘业之论也。觑其根窟则只是自私自利而已。所谓归一者。果与吾儒理一之言。无虚实之判耶。呜呼。吾儒以修己。为安百姓之本。老氏以无为。为民自化之要。佛者以慈悲。为度众生之务。其济物之心。几于略同矣。然而吾儒之修己也。心必求正。意必求诚。以为修身之本。而推以及于百姓。未有源不清而流洁者也。未有表不端而影正者也。故其先治在我者如此。孟子以物正本乎正己。曾子以治平本乎修身者。皆以此也。而老氏之化民也。直曰无为。若如此说。礼乐文物。无所寓焉。典章法度。无所施焉。经纶致泽之具。废矣。养生送死之礼。堙矣。乌可哉。况其所谓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者。出于权谋。而为后来诈力辈之藉口。其不可比称于吾儒修己治人之道决矣。佛者之
合。敛之则在方寸者此也。而老氏之一者。不过清虚之物事也。谷神之诡诀也。厌烦就简。讳有指无。而道德五千之言。半是捭阖之论也。半是刑名之说也。语其仁义。则只是煦煦焉孑孑焉。所谓抱一者。果与吾儒贯一之道。无黑白之辨耶。佛者之一者。亦不过泡沤之法门耳。梦幻之教宗耳。以人彝天常。为尘根妄想。而世界三千之说。一则菩提圆觉之意也。一则魔障缘业之论也。觑其根窟则只是自私自利而已。所谓归一者。果与吾儒理一之言。无虚实之判耶。呜呼。吾儒以修己。为安百姓之本。老氏以无为。为民自化之要。佛者以慈悲。为度众生之务。其济物之心。几于略同矣。然而吾儒之修己也。心必求正。意必求诚。以为修身之本。而推以及于百姓。未有源不清而流洁者也。未有表不端而影正者也。故其先治在我者如此。孟子以物正本乎正己。曾子以治平本乎修身者。皆以此也。而老氏之化民也。直曰无为。若如此说。礼乐文物。无所寓焉。典章法度。无所施焉。经纶致泽之具。废矣。养生送死之礼。堙矣。乌可哉。况其所谓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者。出于权谋。而为后来诈力辈之藉口。其不可比称于吾儒修己治人之道决矣。佛者之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0L 页
 度众也。惟贵慈悲。若如其术。果能以一念阿弥陀佛。跻大地生灵于极乐世界乎。孟子以子产之济人溱洧。尚谓不知为政。彼黄面瞿昙者。安能以坐算一串珠之法。得人人而度之乎。且使其学得行而父子君臣夫妇之伦。都归亡灭。则天地之间。初无可度之众生矣。又将于何而慈悲耶。其不可拟论于吾儒成己成物之道明矣。噫。吾儒之于二家。冰炭自别。薰莸各判。毫釐毕见其得失矣。本末俱露其邪正矣。执事所谓源头之既甚相近者。以愚观之。千万里之远矣。执事所谓用心之亦不悬殊者。以愚观之。悬天壤之殊矣。执事所谓守约之无异。济物之略同者。以愚观之。率皆大有异而略不同矣。世之学者。舍吾儒而求他术。则愚不知其可也。至若康节以老氏为得易之体。盖以其能合乎屈伸隐见之义也。然朱子斥之以为老子自有老子之体。何尝得易之体。朱子之定论如此。则邵氏之言。自不衬贴矣。伊川以庄子为善形容道体。亦取其天运篇中。天其运地其处之说也。此与孟子所引阳虎为仁不富之语同。非谓其知道也。夫虚灵惺惺等语。皆佛者之所发。而吾儒不嫌用之者以其理同也。彼虽吊诡之客。既能有一斑之窥见道
度众也。惟贵慈悲。若如其术。果能以一念阿弥陀佛。跻大地生灵于极乐世界乎。孟子以子产之济人溱洧。尚谓不知为政。彼黄面瞿昙者。安能以坐算一串珠之法。得人人而度之乎。且使其学得行而父子君臣夫妇之伦。都归亡灭。则天地之间。初无可度之众生矣。又将于何而慈悲耶。其不可拟论于吾儒成己成物之道明矣。噫。吾儒之于二家。冰炭自别。薰莸各判。毫釐毕见其得失矣。本末俱露其邪正矣。执事所谓源头之既甚相近者。以愚观之。千万里之远矣。执事所谓用心之亦不悬殊者。以愚观之。悬天壤之殊矣。执事所谓守约之无异。济物之略同者。以愚观之。率皆大有异而略不同矣。世之学者。舍吾儒而求他术。则愚不知其可也。至若康节以老氏为得易之体。盖以其能合乎屈伸隐见之义也。然朱子斥之以为老子自有老子之体。何尝得易之体。朱子之定论如此。则邵氏之言。自不衬贴矣。伊川以庄子为善形容道体。亦取其天运篇中。天其运地其处之说也。此与孟子所引阳虎为仁不富之语同。非谓其知道也。夫虚灵惺惺等语。皆佛者之所发。而吾儒不嫌用之者以其理同也。彼虽吊诡之客。既能有一斑之窥见道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1H 页
 体者。则圣贤亦何嫌于称许乎。其大公至正。不以人废言。亦可见矣。文中子儒者也。而谓佛为圣人可乎。隋阙献策。昧行藏之道。河汾教授。多驳杂之讥。学识之不纯。于此可想。则认瓦为玉。诚无足怪。而古人之指为霸儒不亦宜乎。尹和靖贤者也。而以观音为贤者可乎。六经圣贤之训。如诵己言。则道德可谓醇矣。学术可谓正矣。而犹有此一字之误称。虽为萱堂所拘。不得直伸己见。而尚足为大德之一眚也。谢显道程门亲炙之高弟也。讲劘于函丈之间。论辨于春风之座者。不为不多。而其为学不免淫于老佛。鹦鹉能言之讥。自蹈而不悟。二氏之难辨而易惑者。信乎至此。而窃为上蔡惜之也。陆子静可谓笃实之士也。平日言论。动引孟子。扬眉瞬目。呵佛骂祖。而独其遗却下学而但务上达。阙此穷格而惟事顿悟。伊蒲气味。换骨出来。鹅湖之会。拍头胡叫。此朱子所以有日征月迈之语。而江西之学。至今流毒。可胜叹哉。宜阳谋士纯用黄老。而儒者气像之语。见许于南轩。则岂非以从容周旋。不露踪迹而云乎。然追羽固陵之计。程子以为不仁甚矣。安可以南轩一时之评。掩程子不易之论也。眉山学士所到参禅。而近世名卿之称。见
体者。则圣贤亦何嫌于称许乎。其大公至正。不以人废言。亦可见矣。文中子儒者也。而谓佛为圣人可乎。隋阙献策。昧行藏之道。河汾教授。多驳杂之讥。学识之不纯。于此可想。则认瓦为玉。诚无足怪。而古人之指为霸儒不亦宜乎。尹和靖贤者也。而以观音为贤者可乎。六经圣贤之训。如诵己言。则道德可谓醇矣。学术可谓正矣。而犹有此一字之误称。虽为萱堂所拘。不得直伸己见。而尚足为大德之一眚也。谢显道程门亲炙之高弟也。讲劘于函丈之间。论辨于春风之座者。不为不多。而其为学不免淫于老佛。鹦鹉能言之讥。自蹈而不悟。二氏之难辨而易惑者。信乎至此。而窃为上蔡惜之也。陆子静可谓笃实之士也。平日言论。动引孟子。扬眉瞬目。呵佛骂祖。而独其遗却下学而但务上达。阙此穷格而惟事顿悟。伊蒲气味。换骨出来。鹅湖之会。拍头胡叫。此朱子所以有日征月迈之语。而江西之学。至今流毒。可胜叹哉。宜阳谋士纯用黄老。而儒者气像之语。见许于南轩。则岂非以从容周旋。不露踪迹而云乎。然追羽固陵之计。程子以为不仁甚矣。安可以南轩一时之评。掩程子不易之论也。眉山学士所到参禅。而近世名卿之称。见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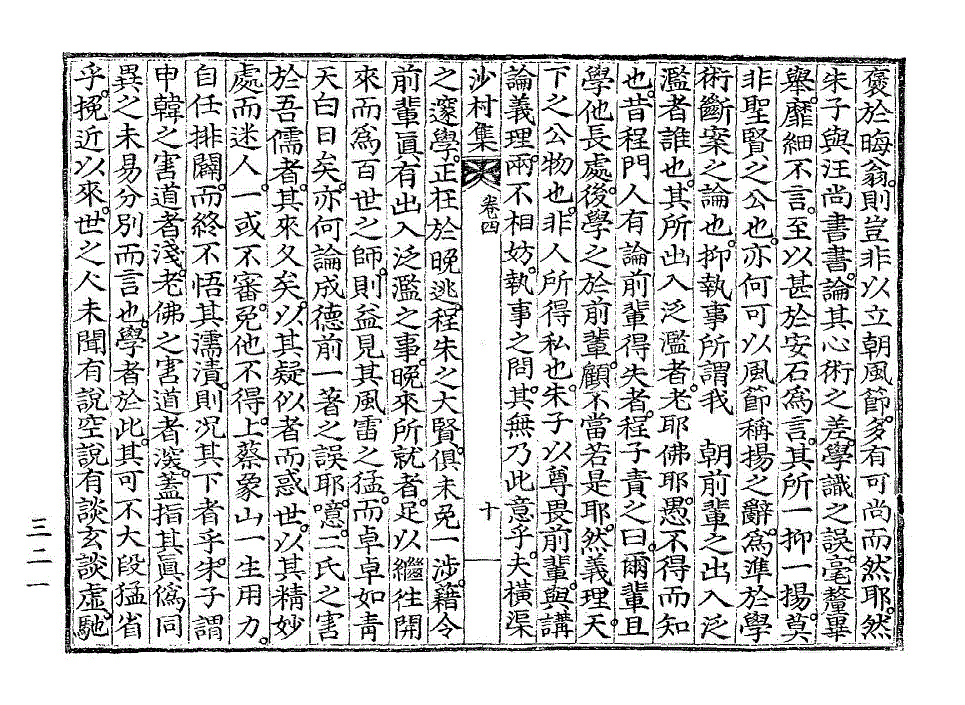 褒于晦翁。则岂非以立朝风节。多有可尚而然耶。然朱子与汪尚书书。论其心术之差。学识之误。毫釐毕举。靡细不言。至以甚于安石为言。其所一抑一扬。莫非圣贤之公也。亦何可以风节称扬之辞。为准于学术断案之论也。抑执事所谓我 朝前辈之出入泛滥者谁也。其所出入泛滥者。老耶佛耶。愚不得而知也。昔程门人有论前辈得失者。程子责之曰。尔辈且学他长处。后学之于前辈。顾不当若是耶。然义理。天下之公物也。非人所得私也。朱子以尊畏前辈。与讲论义理。两不相妨。执事之问。其无乃此意乎。夫横渠之邃学。正在于晚逃。程朱之大贤。俱未免一涉。藉令前辈真有出入泛滥之事。晚来所就者。足以继往开来而为百世之师。则益见其风雷之猛。而卓卓如青天白日矣。亦何论成德前一著之误耶。噫。二氏之害于吾儒者。其来久矣。以其疑似者而惑世。以其精妙处而迷人。一或不审。免他不得。上蔡象山一生用力。自任排辟。而终不悟其濡渍。则况其下者乎。朱子谓申韩之害道者浅。老佛之害道者深。盖指其真伪同异之未易分别而言也。学者于此。其可不大段猛省乎。挽近以来。世之人未闻有说空说有谈玄谈虚。驰
褒于晦翁。则岂非以立朝风节。多有可尚而然耶。然朱子与汪尚书书。论其心术之差。学识之误。毫釐毕举。靡细不言。至以甚于安石为言。其所一抑一扬。莫非圣贤之公也。亦何可以风节称扬之辞。为准于学术断案之论也。抑执事所谓我 朝前辈之出入泛滥者谁也。其所出入泛滥者。老耶佛耶。愚不得而知也。昔程门人有论前辈得失者。程子责之曰。尔辈且学他长处。后学之于前辈。顾不当若是耶。然义理。天下之公物也。非人所得私也。朱子以尊畏前辈。与讲论义理。两不相妨。执事之问。其无乃此意乎。夫横渠之邃学。正在于晚逃。程朱之大贤。俱未免一涉。藉令前辈真有出入泛滥之事。晚来所就者。足以继往开来而为百世之师。则益见其风雷之猛。而卓卓如青天白日矣。亦何论成德前一著之误耶。噫。二氏之害于吾儒者。其来久矣。以其疑似者而惑世。以其精妙处而迷人。一或不审。免他不得。上蔡象山一生用力。自任排辟。而终不悟其濡渍。则况其下者乎。朱子谓申韩之害道者浅。老佛之害道者深。盖指其真伪同异之未易分别而言也。学者于此。其可不大段猛省乎。挽近以来。世之人未闻有说空说有谈玄谈虚。驰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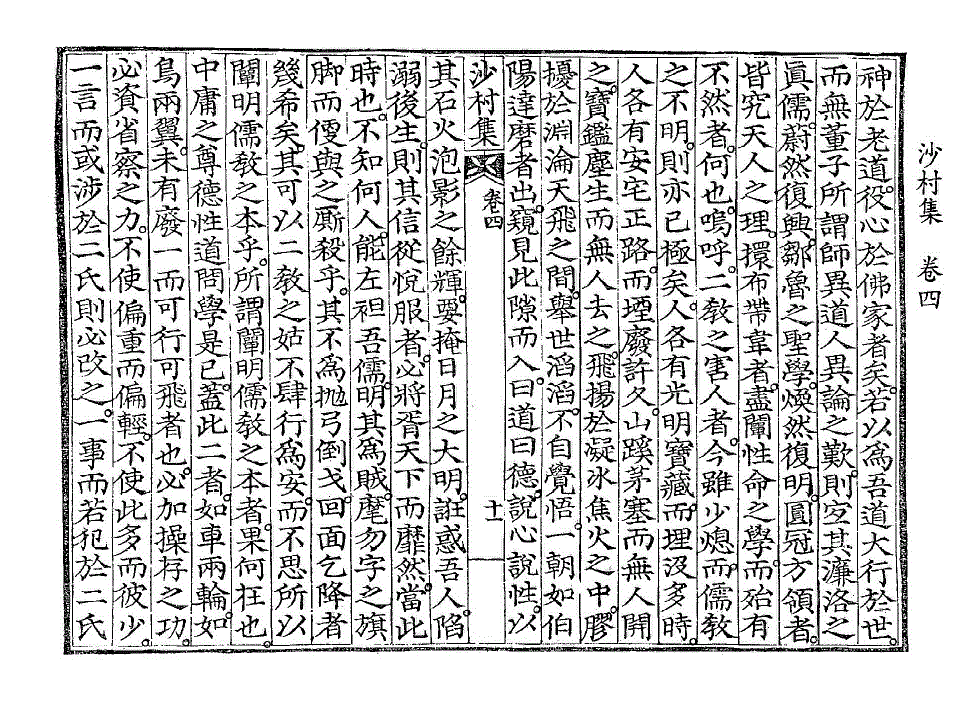 神于老道。役心于佛家者矣。若以为吾道大行于世。而无董子所谓师异道人异论之叹。则宜其濂洛之真儒。蔚然复兴。邹鲁之圣学。焕然复明。圆冠方领者。皆究天人之理。擐布带韦者。尽阐性命之学。而殆有不然者。何也。呜呼。二教之害人者。今虽少熄。而儒教之不明。则亦已极矣。人各有光明宝藏。而埋没多时。人各有安宅正路。而堙废许久。山蹊茅塞而无人开之。宝鉴尘生而无人去之。飞扬于凝冰焦火之中。胶扰于渊沦天飞之间。举世滔滔。不自觉悟。一朝如伯阳达磨者出。窥见此隙而入。曰道曰德。说心说性。以其石火泡影之馀辉。要掩日月之大明。诳惑吾人。陷溺后生。则其信从悦服者。必将胥天下而靡然。当此时也。不知何人。能左袒吾儒。明其为贼。麾勿字之旗脚而便与之厮杀乎。其不为抛弓倒戈。回面乞降者几希矣。其可以二教之姑不肆行为安。而不思所以阐明儒教之本乎。所谓阐明儒教之本者。果何在也。中庸之尊德性道问学是已。盖此二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一而可行可飞者也。必加操存之功。必资省察之力。不使偏重而偏轻。不使此多而彼少。一言而或涉于二氏则必改之。一事而若犯于二氏
神于老道。役心于佛家者矣。若以为吾道大行于世。而无董子所谓师异道人异论之叹。则宜其濂洛之真儒。蔚然复兴。邹鲁之圣学。焕然复明。圆冠方领者。皆究天人之理。擐布带韦者。尽阐性命之学。而殆有不然者。何也。呜呼。二教之害人者。今虽少熄。而儒教之不明。则亦已极矣。人各有光明宝藏。而埋没多时。人各有安宅正路。而堙废许久。山蹊茅塞而无人开之。宝鉴尘生而无人去之。飞扬于凝冰焦火之中。胶扰于渊沦天飞之间。举世滔滔。不自觉悟。一朝如伯阳达磨者出。窥见此隙而入。曰道曰德。说心说性。以其石火泡影之馀辉。要掩日月之大明。诳惑吾人。陷溺后生。则其信从悦服者。必将胥天下而靡然。当此时也。不知何人。能左袒吾儒。明其为贼。麾勿字之旗脚而便与之厮杀乎。其不为抛弓倒戈。回面乞降者几希矣。其可以二教之姑不肆行为安。而不思所以阐明儒教之本乎。所谓阐明儒教之本者。果何在也。中庸之尊德性道问学是已。盖此二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一而可行可飞者也。必加操存之功。必资省察之力。不使偏重而偏轻。不使此多而彼少。一言而或涉于二氏则必改之。一事而若犯于二氏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2L 页
 则必去之。然后方可尽吾儒之事业。而无外染之患矣。是故。朱夫子一生用力于此。才觉有一边偏重者。未尝不痛革而勇改焉。见象山之从事于顿悟之学。则辄谓浸淫禅旨。见末学之缭绕于文义之末。则又颇指示本体。下学而上达。直内而方外。知行兼全。功力俱到。此朱子之学所以集群儒大成。而彼二氏者。举不能遁形而隐情者。苟或偏主于尊德性工夫。则其终也必谓穷格为支离。谓事物为烦碎。而骛于捷径。直指本心。虽竟臻妙觉之域。而不过为江西别派之学矣。其何异于二氏清净寂灭之教哉。此吾儒之必以道问学兼行者也。又或偏务于道问学工夫。则其末也必徒事乎训诂名目。但务于专门章句。而根本田地。全昧吃紧。虽仅得钻研之效。而亦不过为双峰北溪之学矣。安能辨夫二氏心学同异之际乎。此吾儒之必以尊德性并举者也。虽然。尊德性道问学。自有本末先后之次第。而不可躐等者也。语其体用之本末。则尊德性为本。而道问学为末。语其入道之先后。则道问学为先。而尊德性为后。大学所谓格物居诚意之先。孟子所谓博学居说约之先。此岂非成就吾儒之阶级而剖析二氏之明诀乎。二者之在我
则必去之。然后方可尽吾儒之事业。而无外染之患矣。是故。朱夫子一生用力于此。才觉有一边偏重者。未尝不痛革而勇改焉。见象山之从事于顿悟之学。则辄谓浸淫禅旨。见末学之缭绕于文义之末。则又颇指示本体。下学而上达。直内而方外。知行兼全。功力俱到。此朱子之学所以集群儒大成。而彼二氏者。举不能遁形而隐情者。苟或偏主于尊德性工夫。则其终也必谓穷格为支离。谓事物为烦碎。而骛于捷径。直指本心。虽竟臻妙觉之域。而不过为江西别派之学矣。其何异于二氏清净寂灭之教哉。此吾儒之必以道问学兼行者也。又或偏务于道问学工夫。则其末也必徒事乎训诂名目。但务于专门章句。而根本田地。全昧吃紧。虽仅得钻研之效。而亦不过为双峰北溪之学矣。安能辨夫二氏心学同异之际乎。此吾儒之必以尊德性并举者也。虽然。尊德性道问学。自有本末先后之次第。而不可躐等者也。语其体用之本末。则尊德性为本。而道问学为末。语其入道之先后。则道问学为先。而尊德性为后。大学所谓格物居诚意之先。孟子所谓博学居说约之先。此岂非成就吾儒之阶级而剖析二氏之明诀乎。二者之在我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3H 页
 者既尽。则于天下蚕丝牛毛之义理。无所不通。无所不烛。极高明而致广大者。不外于此。如此则可以穷二氏之巢穴。而不为其所染也。何者。彼以玄虚立言。而我以真实为学。彼以寂灭驾说。而我以诚正为教。彼以遗弃事物相尚。而我以穷理格物为本。彼以绝去伦常相高。而我以君臣父子为则。彼则惟贵自私一己。而我则有经纶设施之业。彼则徒贵灵明知觉。而我则该性命理气而言。彼二氏者。有体无用。而我则兼体用而行之。彼二氏者。贵道贱器。而我则合道器而一之。以至源头之说。自见真假。治心之法。各有虚实。守约之工。由是而判邪正矣。济物之道。由是而别霄壤矣。似是者益见其非而不相眩矣。似同者益见其异而不相混矣。尚安有害道贼德之患哉。昔韩文公之作原道篇也。其斥二氏之说。不为不至。而程子犹以无头讥之。盖谓其阙格致也。于此益见德性问学之为吾儒第一法门。而非二氏所可拟论也。愚未知今日之士。果能有用力于此者乎。如其未也。执事胡不勉一世之士。专心于此。致志于此。于道问学也。毫分焉缕析焉。于尊德性也。鉴空焉水止焉。使吾之学。置水不漏。使吾之道。攧扑不破。表里洞彻。本末
者既尽。则于天下蚕丝牛毛之义理。无所不通。无所不烛。极高明而致广大者。不外于此。如此则可以穷二氏之巢穴。而不为其所染也。何者。彼以玄虚立言。而我以真实为学。彼以寂灭驾说。而我以诚正为教。彼以遗弃事物相尚。而我以穷理格物为本。彼以绝去伦常相高。而我以君臣父子为则。彼则惟贵自私一己。而我则有经纶设施之业。彼则徒贵灵明知觉。而我则该性命理气而言。彼二氏者。有体无用。而我则兼体用而行之。彼二氏者。贵道贱器。而我则合道器而一之。以至源头之说。自见真假。治心之法。各有虚实。守约之工。由是而判邪正矣。济物之道。由是而别霄壤矣。似是者益见其非而不相眩矣。似同者益见其异而不相混矣。尚安有害道贼德之患哉。昔韩文公之作原道篇也。其斥二氏之说。不为不至。而程子犹以无头讥之。盖谓其阙格致也。于此益见德性问学之为吾儒第一法门。而非二氏所可拟论也。愚未知今日之士。果能有用力于此者乎。如其未也。执事胡不勉一世之士。专心于此。致志于此。于道问学也。毫分焉缕析焉。于尊德性也。鉴空焉水止焉。使吾之学。置水不漏。使吾之道。攧扑不破。表里洞彻。本末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3L 页
 一致。然后以之而针砭二氏。以之而排辟二氏。则彼二氏者。必将收舌敛唇。而不敢乱真矣。非徒不乱也。必将同消共灭。而不复作矣。非徒不作也。必将潜移默化于吾儒之教矣。执事所谓无他歧之惑。而会归一道者。愚恐不可外此而求也。呜呼。执事以研穷心性。究赜源流之意。许于愚生。以无拘科套。妙论详说之语。勉于愚生。而愚生所答。略绰如此。草率如此。其忝吾儒之名。而负执事之望多矣。愧悚之极。无以为喻。第漏钟之限。异于常日。程式之文。殊于简牍。则难乎毕阐儒教之蕴奥。而尽摅二氏之隐微也。辞将毕矣。篇已就矣。敢复以敬之一字尾之曰。夫敬是常惺惺法也。主一无适之谓也。尊德性而非敬。则不免二三而屋漏有愧矣。道问学而非敬。则不免间断而纤毫莫察矣。故程子每说敬字。学者于主敬工夫。用力而不辍。则吾儒之能事毕矣。二氏之为教。不难辨矣。谨对。
一致。然后以之而针砭二氏。以之而排辟二氏。则彼二氏者。必将收舌敛唇。而不敢乱真矣。非徒不乱也。必将同消共灭。而不复作矣。非徒不作也。必将潜移默化于吾儒之教矣。执事所谓无他歧之惑。而会归一道者。愚恐不可外此而求也。呜呼。执事以研穷心性。究赜源流之意。许于愚生。以无拘科套。妙论详说之语。勉于愚生。而愚生所答。略绰如此。草率如此。其忝吾儒之名。而负执事之望多矣。愧悚之极。无以为喻。第漏钟之限。异于常日。程式之文。殊于简牍。则难乎毕阐儒教之蕴奥。而尽摅二氏之隐微也。辞将毕矣。篇已就矣。敢复以敬之一字尾之曰。夫敬是常惺惺法也。主一无适之谓也。尊德性而非敬。则不免二三而屋漏有愧矣。道问学而非敬。则不免间断而纤毫莫察矣。故程子每说敬字。学者于主敬工夫。用力而不辍。则吾儒之能事毕矣。二氏之为教。不难辨矣。谨对。[君臣服制]
问。君臣服制。礼之大者。少有所忽。礼以之坏矣。礼坏而国治者。未之有也。可不慎欤。其斩衰之义何据。方丧之称何取。臣服见于仪礼。则夏商之盛际。其所制服者。何欤。短丧肇于文帝。则嬴
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4H 页
 秦之无礼。亦服斩衰之制欤。虞典之说。百姓如丧考妣。周公之制。庶人止服三月者。既自不同。而至于语类。则以通天下为天子三年之说。又不以为非后来定制。其将何所取舍欤。仪礼则于杖元无区别之论。礼记则以杖只许达官之长者。亦似有异。而至于疏家。则又以为服斩者。皆当备服衰杖。而其所谓长者。不复明言。后来从违。如何能免做错欤。大夫之已致仕者。仕而不及大夫者。其服何如。大夫而未接见。仕而未有禄者。亦皆服本服欤。天子之丧。世子无服。则陪臣之为天子。亦皆无服。公卿之妻。君丧有服。则王女之嫁公卿。亦服其服欤。为君之丧。一如为父。则臣之为母后。亦同为母。以父之尊。既服其子。则君之为臣也。亦有所服欤。宋孝独断。能服三年。而衰裳之制。固多差误于古制。其误处可得闻欤。朱子服议最详论说。而节目之间。不能无异于古礼。其异者。可历言欤。方其谅闇而视事之白衣布帽。其亦有据。既同父斩。而燕居之绢巾凉衫。必有其意。皆可详论欤。淳熙之制。其终遵守而丧服之劄。果在何时欤。小祥之日。
秦之无礼。亦服斩衰之制欤。虞典之说。百姓如丧考妣。周公之制。庶人止服三月者。既自不同。而至于语类。则以通天下为天子三年之说。又不以为非后来定制。其将何所取舍欤。仪礼则于杖元无区别之论。礼记则以杖只许达官之长者。亦似有异。而至于疏家。则又以为服斩者。皆当备服衰杖。而其所谓长者。不复明言。后来从违。如何能免做错欤。大夫之已致仕者。仕而不及大夫者。其服何如。大夫而未接见。仕而未有禄者。亦皆服本服欤。天子之丧。世子无服。则陪臣之为天子。亦皆无服。公卿之妻。君丧有服。则王女之嫁公卿。亦服其服欤。为君之丧。一如为父。则臣之为母后。亦同为母。以父之尊。既服其子。则君之为臣也。亦有所服欤。宋孝独断。能服三年。而衰裳之制。固多差误于古制。其误处可得闻欤。朱子服议最详论说。而节目之间。不能无异于古礼。其异者。可历言欤。方其谅闇而视事之白衣布帽。其亦有据。既同父斩。而燕居之绢巾凉衫。必有其意。皆可详论欤。淳熙之制。其终遵守而丧服之劄。果在何时欤。小祥之日。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4L 页
 不当从吉者。孰主此议。而易月之后。权用黑带者。发之何人欤。猗欤。我 朝素称礼义。 英庙制礼。郁郁彬彬。一部五礼仪。永为 列圣之所受用。而其服制一篇。先正或以遵朱子之意。亟称之。乌帽之制。儒臣或谓非古礼之正。请改之。儒贤之论。必各有见。而至于百官之服。则布团领之斩边。布裹帽而带麻。非宋之视朝服。又不是古丧服。则 祖宗之制。其果无所据欤。粤若我 先大王圣学高明。睿断出天。丧服之节。克遵古制。一洗千古之陋习。以定百王之成法。可谓无有馀憾矣。第大臣献议。该曹覆启。而临丧仓卒。或欠致详。仪注之间。不无议者之纷纷。或者谓丧冠之制。一二梁非古也。或者谓承衰之服。终不可无者也。或者谓追服之节不论。而多有窒碍。或者谓儒生之衰不成。而无所依据。或者谓祥衰不练。终见与大功熟布之说相乖。或者谓麻绞变布。不可以公士众臣之礼为据。或者谓熟麻代葛甚苟简。或者谓冠缨用布亦可疑。未知 朝家定制。自无差谬。而或者诸说。未免苛摘耶。抑或说尽有据于先儒礼说。而朝制
不当从吉者。孰主此议。而易月之后。权用黑带者。发之何人欤。猗欤。我 朝素称礼义。 英庙制礼。郁郁彬彬。一部五礼仪。永为 列圣之所受用。而其服制一篇。先正或以遵朱子之意。亟称之。乌帽之制。儒臣或谓非古礼之正。请改之。儒贤之论。必各有见。而至于百官之服。则布团领之斩边。布裹帽而带麻。非宋之视朝服。又不是古丧服。则 祖宗之制。其果无所据欤。粤若我 先大王圣学高明。睿断出天。丧服之节。克遵古制。一洗千古之陋习。以定百王之成法。可谓无有馀憾矣。第大臣献议。该曹覆启。而临丧仓卒。或欠致详。仪注之间。不无议者之纷纷。或者谓丧冠之制。一二梁非古也。或者谓承衰之服。终不可无者也。或者谓追服之节不论。而多有窒碍。或者谓儒生之衰不成。而无所依据。或者谓祥衰不练。终见与大功熟布之说相乖。或者谓麻绞变布。不可以公士众臣之礼为据。或者谓熟麻代葛甚苟简。或者谓冠缨用布亦可疑。未知 朝家定制。自无差谬。而或者诸说。未免苛摘耶。抑或说尽有据于先儒礼说。而朝制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5H 页
 果不无差误耶。抑不知朝制与或说。或得或失。各有取舍者耶。诸生必有素讲于三百三千之礼。而今日服制。亦必有讲明之者。须无袭科套。考据礼书。逐条而详说之。主司当转闻而采用之。
果不无差误耶。抑不知朝制与或说。或得或失。各有取舍者耶。诸生必有素讲于三百三千之礼。而今日服制。亦必有讲明之者。须无袭科套。考据礼书。逐条而详说之。主司当转闻而采用之。对。呜呼。人臣之致哀君上之服。不行也久矣。祥禫之礼废。而世昧乎齐疏之制。易月之规俑。而人恬于沿袭之谬。人彝天常。由是而渐就斁败。节文仪则。职此而日益坏崩。其不知者肆然红紫而无忌。其稍知者不过襕幞而自处。率不知天经地谊之截然而不可紊。则古先王通丧之制。几乎扫地尽矣。噫。五等之隆杀。莫非丧服也。自三月而五月。自五月而九月。自九月而期年。自期年而三年。皆圣人所以参酌情文。区别轻重。以尽夫礼制者。而惟三年之丧。通上下达贵贱。子之于父也。臣之于君也。共循一道。本无二致。夫既策名许身。委质为臣。则大分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其所以伸情礼而展哀敬者。宜与顾我复我之亲。其服一也。而世之服君丧者。反视功缌之下。则其反常而悖义也何如哉。朱子以寝苫枕块。面墨颜戚之节。为与父丧差有不同。而古者人臣。有父服而
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5L 页
 遭君丧者。必之君所。必服君服。压于至尊。而不得伸其私情。此则义掩于恩。而君丧视父丧为尤重者也。春秋以来。此礼弁髦。嗣君之谅闇三年者。既不得见矣。况望臣下之独能行古礼。终君服者乎。因讹踵陋之风。甚至于埋衰而即吉。滔滔一辙。无古无今。终未有一洗污习。快复古制者。此政朱子所谓人君自无孝敬之心。人臣为婚姻享祀聚会之节。而不欲复古者也。是故。晋武欲行三年。而为群下所拘。才葬而止。魏文将服三年。而亦为诸臣所争。期而行禫。则当时臣服之不终。盖可知矣。然而视世之君臣锦稻。上下贸贸者。不啻有间。故先儒之论。未尝不惜其不能行。而多其欲行。人君有能拔出流俗。断行古礼。使君臣之服。一归大正。则圣贤所以称颂褒美。叹服赞扬者。必将与三代制礼之圣王。同条共论。而晋魏斑驳之制。有不足道者矣。呜呼。今日邦丧之礼。可谓大正矣。百官环绖。万姓带麻。班哭巷恸。皆有仪节。阙文旷典。无复遗漏。环东土数千里含生之类。皆知有君服之重。而得以少伸其臣子区区之忱。日月几何。 练事倏过。靡逮之痛。益复难抑。乃者执事先生。策我承学之士。而首以君臣服制之说。揭为明问中第一义。究
遭君丧者。必之君所。必服君服。压于至尊。而不得伸其私情。此则义掩于恩。而君丧视父丧为尤重者也。春秋以来。此礼弁髦。嗣君之谅闇三年者。既不得见矣。况望臣下之独能行古礼。终君服者乎。因讹踵陋之风。甚至于埋衰而即吉。滔滔一辙。无古无今。终未有一洗污习。快复古制者。此政朱子所谓人君自无孝敬之心。人臣为婚姻享祀聚会之节。而不欲复古者也。是故。晋武欲行三年。而为群下所拘。才葬而止。魏文将服三年。而亦为诸臣所争。期而行禫。则当时臣服之不终。盖可知矣。然而视世之君臣锦稻。上下贸贸者。不啻有间。故先儒之论。未尝不惜其不能行。而多其欲行。人君有能拔出流俗。断行古礼。使君臣之服。一归大正。则圣贤所以称颂褒美。叹服赞扬者。必将与三代制礼之圣王。同条共论。而晋魏斑驳之制。有不足道者矣。呜呼。今日邦丧之礼。可谓大正矣。百官环绖。万姓带麻。班哭巷恸。皆有仪节。阙文旷典。无复遗漏。环东土数千里含生之类。皆知有君服之重。而得以少伸其臣子区区之忱。日月几何。 练事倏过。靡逮之痛。益复难抑。乃者执事先生。策我承学之士。而首以君臣服制之说。揭为明问中第一义。究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6H 页
 极于古今之常变。发难于典礼之同异。以至今日丧服中节目之未尽归正者。仪注之未尽合礼者。靡不详说。思与诸生。折衷而绵蕝之。噫嘻。意甚盛也。盖欲讲明乎圣人之遗制。以对扬 先大王之志事也。愚于平日。未尝学礼。何足以与论邦家之大礼乎。第得于师友讲磨者则有之。敢不搜集旧闻。悉心仰复。以备高明之裁择焉。窃谓子夏传曰。丧君三年。此君臣服制之所以为礼之大者也。盖君臣以义合者也。义之所在。礼由生焉。丧则致哀。致哀则有服。有服则必为之服斩。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祥。又中月而禫。然后合乎天理。尽乎人情。是以为人臣者。于君父之丧。循是礼而行之。持是服而居之。衰其衣裳而尽三踊之制。麻其绖带而守一定之规。斩焉累焉之貌。不变于钻燧之累改。慨然廓然之痛。渐阕于霜露之再降。服事之义。由是而无憾。哀慕之诚。由是而得展。三代与共而未尝废也。万世攸遵而不可违也。则信乎礼之大者无过于此也。苟于此。一有所少忽。则达丧之义紊而常服之制不行。袭谬之风成而自尽之道有歉。天人之大经大防。因此而坏矣。大经大防坏矣。而其国能治者。从古以来未之有焉。世之当大事者。
极于古今之常变。发难于典礼之同异。以至今日丧服中节目之未尽归正者。仪注之未尽合礼者。靡不详说。思与诸生。折衷而绵蕝之。噫嘻。意甚盛也。盖欲讲明乎圣人之遗制。以对扬 先大王之志事也。愚于平日。未尝学礼。何足以与论邦家之大礼乎。第得于师友讲磨者则有之。敢不搜集旧闻。悉心仰复。以备高明之裁择焉。窃谓子夏传曰。丧君三年。此君臣服制之所以为礼之大者也。盖君臣以义合者也。义之所在。礼由生焉。丧则致哀。致哀则有服。有服则必为之服斩。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祥。又中月而禫。然后合乎天理。尽乎人情。是以为人臣者。于君父之丧。循是礼而行之。持是服而居之。衰其衣裳而尽三踊之制。麻其绖带而守一定之规。斩焉累焉之貌。不变于钻燧之累改。慨然廓然之痛。渐阕于霜露之再降。服事之义。由是而无憾。哀慕之诚。由是而得展。三代与共而未尝废也。万世攸遵而不可违也。则信乎礼之大者无过于此也。苟于此。一有所少忽。则达丧之义紊而常服之制不行。袭谬之风成而自尽之道有歉。天人之大经大防。因此而坏矣。大经大防坏矣。而其国能治者。从古以来未之有焉。世之当大事者。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6L 页
 其可不致慎于此哉。虽然。服制之设。其本在戚。礼义之出。其原缘情。服制虽行。而不尽乎哀痛之实。则安用彼服制哉。礼义虽明。而徒事于文具之末。则安用彼礼义哉。孔子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然则尽在我之诚孝。致群臣之观感。勉循服制之正。率归礼义之衷者。顾不在于在上者乎。诚能以羹墙之慕。为锡类之孝。推茕恤之哀。尽维则之道。则人臣服君之礼。粹然一出于正。而可以俟百世质圣人而不悖矣。故曰是在世子。故曰是诚在我。请因明问而陈之。斩衰之斩字。先儒谓斩斩然痛甚之意也。故其服之制。不缉边焉。其取义也如此而已。方丧之方字。古人谓比方而同之之意也。故服君之丧。与父丧同。其取称也。若是而已。臣为君服。始见于周公所撰之仪礼。而前乎此则不见。愚未知夏商之际。其为服何居。夫子生于周末。去二代不远也。犹曰夏礼杞不足徵也。殷礼宋不足徵也。则况生千万代之后。以謏闻浅识。何敢强探微茫。容易臆对乎。第以出于传记者观之。伯益之避启让位也。在于禹丧三年之后。箕子,微子之素车白马。古人亦谓服纣之丧。太甲居桐之日。伊尹仲虺之辈。岂可曰嘉服而
其可不致慎于此哉。虽然。服制之设。其本在戚。礼义之出。其原缘情。服制虽行。而不尽乎哀痛之实。则安用彼服制哉。礼义虽明。而徒事于文具之末。则安用彼礼义哉。孔子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然则尽在我之诚孝。致群臣之观感。勉循服制之正。率归礼义之衷者。顾不在于在上者乎。诚能以羹墙之慕。为锡类之孝。推茕恤之哀。尽维则之道。则人臣服君之礼。粹然一出于正。而可以俟百世质圣人而不悖矣。故曰是在世子。故曰是诚在我。请因明问而陈之。斩衰之斩字。先儒谓斩斩然痛甚之意也。故其服之制。不缉边焉。其取义也如此而已。方丧之方字。古人谓比方而同之之意也。故服君之丧。与父丧同。其取称也。若是而已。臣为君服。始见于周公所撰之仪礼。而前乎此则不见。愚未知夏商之际。其为服何居。夫子生于周末。去二代不远也。犹曰夏礼杞不足徵也。殷礼宋不足徵也。则况生千万代之后。以謏闻浅识。何敢强探微茫。容易臆对乎。第以出于传记者观之。伯益之避启让位也。在于禹丧三年之后。箕子,微子之素车白马。古人亦谓服纣之丧。太甲居桐之日。伊尹仲虺之辈。岂可曰嘉服而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7H 页
 居也。高宗谅闇之时。傅说甘盘之徒。岂可曰华饰而行也。其时制度。虽不可考。而其所以服君者。则愚敢为执事指掌也。短丧之制。肇创于汉文临崩之遗诏。而上乎此则无称。愚未知无礼之秦。亦能行斩衰否也。然以见于经史者證之。滕君之行古丧礼也。父兄百官之言曰。吾先君莫之行也。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宰我孔门之升堂也。犹欲短之。公孙丑孟氏之高弟也。尚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己云尔。则短丧之风。不肇于汉文。而始俑于列国矣。秦本列国之一。而弃礼义之风。尚夷狄之习。沙丘之崩。至于载鲍辒辌。而秘不发丧。则曾谓以胡亥,斯高之徒。而反能服先王斩衰之制乎。以见于虞典者观之。尧崩而百姓如丧考妣。此则言畿内民庶之丧制也。以出于周制者论之。君丧而庶人只服齐衰三月。此则与公卿大夫而有间矣。二说既相矛盾。而至于语类。则不以通天下三年之说为非。其所取舍若何而可也。夫尧舜周公之制。其有轻重隆杀之不同者。要皆圣人参酌损益之宜也。而若言君臣之大经。则天子之尊无二。溥天之下皆臣。事一之义。本无贵贱。故朱子以为既无本国之君服。又不服至尊。则便是无君。至有循本大
居也。高宗谅闇之时。傅说甘盘之徒。岂可曰华饰而行也。其时制度。虽不可考。而其所以服君者。则愚敢为执事指掌也。短丧之制。肇创于汉文临崩之遗诏。而上乎此则无称。愚未知无礼之秦。亦能行斩衰否也。然以见于经史者證之。滕君之行古丧礼也。父兄百官之言曰。吾先君莫之行也。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宰我孔门之升堂也。犹欲短之。公孙丑孟氏之高弟也。尚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己云尔。则短丧之风。不肇于汉文。而始俑于列国矣。秦本列国之一。而弃礼义之风。尚夷狄之习。沙丘之崩。至于载鲍辒辌。而秘不发丧。则曾谓以胡亥,斯高之徒。而反能服先王斩衰之制乎。以见于虞典者观之。尧崩而百姓如丧考妣。此则言畿内民庶之丧制也。以出于周制者论之。君丧而庶人只服齐衰三月。此则与公卿大夫而有间矣。二说既相矛盾。而至于语类。则不以通天下三年之说为非。其所取舍若何而可也。夫尧舜周公之制。其有轻重隆杀之不同者。要皆圣人参酌损益之宜也。而若言君臣之大经。则天子之尊无二。溥天之下皆臣。事一之义。本无贵贱。故朱子以为既无本国之君服。又不服至尊。则便是无君。至有循本大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7L 页
 正之论。无论士庶军民。而当服斩衰。此诚穷源到底之说也。后来受用。恐不外此。若曰有乖于周公古礼。则抑有说焉。夫古今异宜。常变无穷。而礼有时而推移。古者妇人为舅姑服期。而朱子于家礼。从贞观礼三年之制。至今守之。未闻以悖于古礼为言。则至于臣服。何独以三月之制行之而不遵大正之论乎。以仪礼之制言之。杖之一款。元不区别于贵贱。以戴记之说揆之。杖之授受。只许达官之长。两者亦相拘掣。而若夫疏家。则又谓服斩者。备服衰杖。而所谓达官之长者。不复明言其所从违。何以则免于做错耶。夫杖者。所以齐心而辅病者也。官有尊卑。哀有深浅。故授杖与否。随此而别。仪礼戴记之各异者。不过立言详略之有殊。而朱子谓达官之长者。内则如公,卿,宰执,六曹之长。九寺,五监之长。外则如监司,郡守。皆自通章奏于君者也。其所说出。大煞分明。要使后人。考而无疑。则亦何可以贾氏模糊之说。有难于从违哉。至若大夫之致仕者。即致为臣而归者也。其服为齐衰三月。仕而不及大夫者。即庶人之在官者。而兼府史胥徒之属也。其服亦为齐衰三月。大夫之不接见者。即陪臣而未睹天子者也。本服为缌。而未接见则
正之论。无论士庶军民。而当服斩衰。此诚穷源到底之说也。后来受用。恐不外此。若曰有乖于周公古礼。则抑有说焉。夫古今异宜。常变无穷。而礼有时而推移。古者妇人为舅姑服期。而朱子于家礼。从贞观礼三年之制。至今守之。未闻以悖于古礼为言。则至于臣服。何独以三月之制行之而不遵大正之论乎。以仪礼之制言之。杖之一款。元不区别于贵贱。以戴记之说揆之。杖之授受。只许达官之长。两者亦相拘掣。而若夫疏家。则又谓服斩者。备服衰杖。而所谓达官之长者。不复明言其所从违。何以则免于做错耶。夫杖者。所以齐心而辅病者也。官有尊卑。哀有深浅。故授杖与否。随此而别。仪礼戴记之各异者。不过立言详略之有殊。而朱子谓达官之长者。内则如公,卿,宰执,六曹之长。九寺,五监之长。外则如监司,郡守。皆自通章奏于君者也。其所说出。大煞分明。要使后人。考而无疑。则亦何可以贾氏模糊之说。有难于从违哉。至若大夫之致仕者。即致为臣而归者也。其服为齐衰三月。仕而不及大夫者。即庶人之在官者。而兼府史胥徒之属也。其服亦为齐衰三月。大夫之不接见者。即陪臣而未睹天子者也。本服为缌。而未接见则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8H 页
 无服。仕而未有禄者。违则无服。不违则有三月之服。此皆仪礼之所区别而轻重者也。然若举而律之于朱子大正之论。则有不可胶泥于彼者。何也。古之人臣。国无定主。不可于齐则之楚。不可于宋则之晋。鲁卫郑陈。惟其所适。违君而越境。则不反服。惟录丰恩重者。然后为旧君服三月。而自士以下。违则无服。其等分而渐杀者诚宜。汉唐以来。君臣之重。视古自别。服勤致死而终无违去之道。致政老家。而尚有眷系之念。名分所关。恩义兼至。则其可以列国君臣之礼。槩而论之哉。此服制所以有古今厚薄之异者也。此朱子所以不主三月之说。而必垂大正之论者也。天子之丧。世子无服者。以有继世之道。故出于远嫌也。而诸侯之大夫。于天子其服为缌衰裳。则亦安可谓无服也。公卿命妇从夫服期。则所谓夫人如外宗之为君者也。而王女之嫁公卿者。为父斩衰。为母齐衰。则岂可不服本服。而只服命妇之服乎。臣为君服。一如为父。故其为后服者。为齐衰期年。父之于子。既有其服。故君之于臣。亦有所服。所谓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士疑衰者。此也。宋孝宗力排群议。断行丧礼。大布之衣。能服三年。此朱子所谓寿皇
无服。仕而未有禄者。违则无服。不违则有三月之服。此皆仪礼之所区别而轻重者也。然若举而律之于朱子大正之论。则有不可胶泥于彼者。何也。古之人臣。国无定主。不可于齐则之楚。不可于宋则之晋。鲁卫郑陈。惟其所适。违君而越境。则不反服。惟录丰恩重者。然后为旧君服三月。而自士以下。违则无服。其等分而渐杀者诚宜。汉唐以来。君臣之重。视古自别。服勤致死而终无违去之道。致政老家。而尚有眷系之念。名分所关。恩义兼至。则其可以列国君臣之礼。槩而论之哉。此服制所以有古今厚薄之异者也。此朱子所以不主三月之说。而必垂大正之论者也。天子之丧。世子无服者。以有继世之道。故出于远嫌也。而诸侯之大夫。于天子其服为缌衰裳。则亦安可谓无服也。公卿命妇从夫服期。则所谓夫人如外宗之为君者也。而王女之嫁公卿者。为父斩衰。为母齐衰。则岂可不服本服。而只服命妇之服乎。臣为君服。一如为父。故其为后服者。为齐衰期年。父之于子。既有其服。故君之于臣。亦有所服。所谓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士疑衰者。此也。宋孝宗力排群议。断行丧礼。大布之衣。能服三年。此朱子所谓寿皇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8L 页
 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者也。而独其衰裳之制。与古制有误者多矣。若言其误处。则负版之去。辟领之不存。是也。岂可谓与纯然古丧服同哉。然破去历代之谬典。独守练禫之常制。拔出于因循之馀。自持以古礼之正者。实三代后初见。则亦安得以度数之未尽。而议其大体之尽好哉。朱夫子作为服议。论说最详。斟酌古今。究极是非。循本之语。考文之制。政百代君臣之所当遵行者也。而但其节目之间。与古礼异同者有矣。若言其异者。则冠梁之等级。许婚之渐次。是也。然致隆君父之丧。折衷上下之制。参度乎情文之至。务得于礼典之正者。实与元圣所制。相为表里。则又何可以条例之微有出入而忽其谨守之道哉。朱子谓古者人君行谅闇之礼。故元无所谓视事之服者。后世则此礼不行。而万机之繁。庶务之广。有不可以衰绖屦杖临之。遂制布幞头布公服以视事。此盖后之权制也。执事之问。似若于谅闇方行之中。又著视事之布帽布服者然。无乃偶失于照管耶。抑愚生所见。未免于胶固耶。朱子与余正甫书也。当宁宗嗣服之初。深叹寿皇大布之制不复讲行。而群臣至以红紫临丧。故因正甫襕幞之问。而许服
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者也。而独其衰裳之制。与古制有误者多矣。若言其误处。则负版之去。辟领之不存。是也。岂可谓与纯然古丧服同哉。然破去历代之谬典。独守练禫之常制。拔出于因循之馀。自持以古礼之正者。实三代后初见。则亦安得以度数之未尽。而议其大体之尽好哉。朱夫子作为服议。论说最详。斟酌古今。究极是非。循本之语。考文之制。政百代君臣之所当遵行者也。而但其节目之间。与古礼异同者有矣。若言其异者。则冠梁之等级。许婚之渐次。是也。然致隆君父之丧。折衷上下之制。参度乎情文之至。务得于礼典之正者。实与元圣所制。相为表里。则又何可以条例之微有出入而忽其谨守之道哉。朱子谓古者人君行谅闇之礼。故元无所谓视事之服者。后世则此礼不行。而万机之繁。庶务之广。有不可以衰绖屦杖临之。遂制布幞头布公服以视事。此盖后之权制也。执事之问。似若于谅闇方行之中。又著视事之布帽布服者然。无乃偶失于照管耶。抑愚生所见。未免于胶固耶。朱子与余正甫书也。当宁宗嗣服之初。深叹寿皇大布之制不复讲行。而群臣至以红紫临丧。故因正甫襕幞之问。而许服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9H 页
 绢巾凉衫于燕居。非谓此礼之正也。特其视红紫襕幞则为厚。故以此言之。为复古之渐。观其下小注制古丧服以临。乃为合礼之语。则可知与服议所论。同出于正者。无疑也。绍熙之代服孝宗也。凉衫视事之制。史氏谓出于朱子之言。而朱子犹谓只存影子。其制之未纯可见。而尝观宋史胡纮传。宁宗从纮议期年而释服。则其不能终遵淳熙之制。于此可知也。丧服之劄。论嫡孙承重之礼。辨漆纱浅黄之失。则其在宁宗时者无疑。而宁宗视朝之服。只改以白绫背子,白绫衬衫而止。恶在其从朱子之言也。理宗当宁宗小祥之日。群臣之议。皆欲从吉。而斥其不可者。真西山之疏也。其论与朱子服议略同。则其礼之正。于此可见矣。孝宗在高宗初丧之时。易月之后。权用黑带者。罗点之议也。其说与朱子服议相悖。而我 朝先正又论于 经筵日记矣。其礼之失。何待辨也。猗欤。我 朝素以礼义见称。粤若 英庙撰定礼制。彬乎郁乎。驾轶成周。一部五礼仪。 列圣世传。遵而勿失。守而不挠。制度节文。永为邦家之典则。而其中丧服一篇。退溪则以得朱子之意而亟称之。乌帽之制。杏村则谓非古礼之正而请改之。儒贤所见。若是不同
绢巾凉衫于燕居。非谓此礼之正也。特其视红紫襕幞则为厚。故以此言之。为复古之渐。观其下小注制古丧服以临。乃为合礼之语。则可知与服议所论。同出于正者。无疑也。绍熙之代服孝宗也。凉衫视事之制。史氏谓出于朱子之言。而朱子犹谓只存影子。其制之未纯可见。而尝观宋史胡纮传。宁宗从纮议期年而释服。则其不能终遵淳熙之制。于此可知也。丧服之劄。论嫡孙承重之礼。辨漆纱浅黄之失。则其在宁宗时者无疑。而宁宗视朝之服。只改以白绫背子,白绫衬衫而止。恶在其从朱子之言也。理宗当宁宗小祥之日。群臣之议。皆欲从吉。而斥其不可者。真西山之疏也。其论与朱子服议略同。则其礼之正。于此可见矣。孝宗在高宗初丧之时。易月之后。权用黑带者。罗点之议也。其说与朱子服议相悖。而我 朝先正又论于 经筵日记矣。其礼之失。何待辨也。猗欤。我 朝素以礼义见称。粤若 英庙撰定礼制。彬乎郁乎。驾轶成周。一部五礼仪。 列圣世传。遵而勿失。守而不挠。制度节文。永为邦家之典则。而其中丧服一篇。退溪则以得朱子之意而亟称之。乌帽之制。杏村则谓非古礼之正而请改之。儒贤所见。若是不同沙村集卷之四 第 329L 页
 者何耶。夫五礼仪丧服。虽有茅缠纸裹之讥。而君上所服。则一遵古制。通国白衣之礼。又是汉文以来。始创者也。若夫公除后乌帽。则本非人臣致哀之服。而君服于上。臣除于下。 历朝沿承之弊。有不可以不革。则退溪之称赞。杏村之请改者。各有意义。何必论也。至于百官之服。则诚有异焉。其所以斩边于团领。带麻于布帽者。视其上则公服也。见其下则凶服也。加于首者朝冠也。擐于腰者丧带也。其制斑驳。其礼厖杂。既非宋朝视事之凉衫。又异古礼衰绖之丧服。则愚不敢知 祖宗所制之服。果无所依据者耶。此不过仓卒从俗。因仍苟且。以致其半上落下。此政朱子所谓当时儒臣礼官不能建明。以成一代之制者也。此又朱子所谓其失在于兼尽古今。而不知考得失而去取之者也。恭惟我 先大王圣学高明。洞观于礼制之原。睿断出天。勇革乎踵讹之风。其于邦丧之制。深主朱子之论。 御极之日。特降纶音。讲究节目。俾为定式。 礼陟之后。奉承 遗教。丧服诸节。克循古礼。麻绖之服。遍加于内外之官。上下之职。此即仪礼所谓为君斩衰者也。授杖之 命。举归于藩阃之臣。侍从之列。此即戴记所谓达官之长杖者也。擐
者何耶。夫五礼仪丧服。虽有茅缠纸裹之讥。而君上所服。则一遵古制。通国白衣之礼。又是汉文以来。始创者也。若夫公除后乌帽。则本非人臣致哀之服。而君服于上。臣除于下。 历朝沿承之弊。有不可以不革。则退溪之称赞。杏村之请改者。各有意义。何必论也。至于百官之服。则诚有异焉。其所以斩边于团领。带麻于布帽者。视其上则公服也。见其下则凶服也。加于首者朝冠也。擐于腰者丧带也。其制斑驳。其礼厖杂。既非宋朝视事之凉衫。又异古礼衰绖之丧服。则愚不敢知 祖宗所制之服。果无所依据者耶。此不过仓卒从俗。因仍苟且。以致其半上落下。此政朱子所谓当时儒臣礼官不能建明。以成一代之制者也。此又朱子所谓其失在于兼尽古今。而不知考得失而去取之者也。恭惟我 先大王圣学高明。洞观于礼制之原。睿断出天。勇革乎踵讹之风。其于邦丧之制。深主朱子之论。 御极之日。特降纶音。讲究节目。俾为定式。 礼陟之后。奉承 遗教。丧服诸节。克循古礼。麻绖之服。遍加于内外之官。上下之职。此即仪礼所谓为君斩衰者也。授杖之 命。举归于藩阃之臣。侍从之列。此即戴记所谓达官之长杖者也。擐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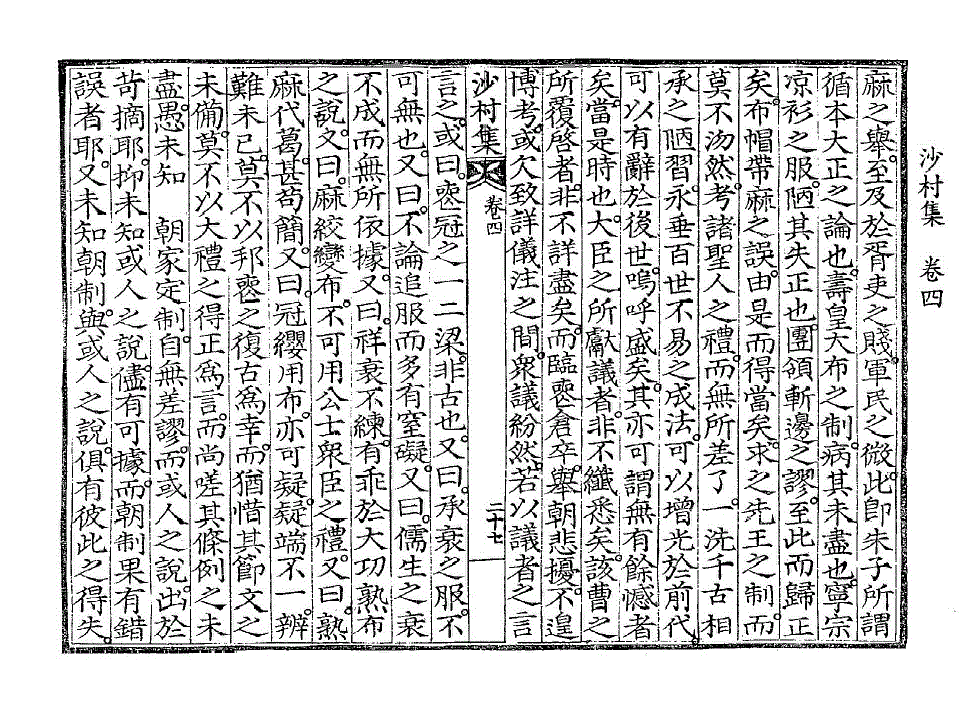 麻之举。至及于胥吏之贱。军民之微。此即朱子所谓循本大正之论也。寿皇大布之制。病其未尽也。宁宗凉衫之服。陋其失正也。团领斩边之谬。至此而归正矣。布帽带麻之误。由是而得当矣。求之先王之制。而莫不吻然。考诸圣人之礼。而无所差了。一洗千古相承之陋习。永垂百世不易之成法。可以增光于前代。可以有辞于后世。呜呼盛矣。其亦可谓无有馀憾者矣。当是时也。大臣之所献议者。非不纤悉矣。该曹之所覆启者。非不详尽矣。而临丧仓卒。举朝悲扰。不遑博考。或欠致详仪注之间。众议纷然。若以议者之言言之。或曰。丧冠之一二梁。非古也。又曰。承衰之服。不可无也。又曰。不论追服而多有窒碍。又曰。儒生之衰不成而无所依据。又曰。祥衰不练。有乖于大功熟布之说。又曰。麻绞变布。不可用公士众臣之礼。又曰。熟麻代葛。甚苟简。又曰。冠缨用布。亦可疑。疑端不一。辨难未已。莫不以邦丧之复古为幸。而犹惜其节文之未备。莫不以大礼之得正为言。而尚嗟其条例之未尽。愚未知 朝家定制。自无差谬。而或人之说。出于苛摘耶。抑未知或人之说。尽有可据。而朝制果有错误者耶。又未知朝制。与或人之说。俱有彼此之得失。
麻之举。至及于胥吏之贱。军民之微。此即朱子所谓循本大正之论也。寿皇大布之制。病其未尽也。宁宗凉衫之服。陋其失正也。团领斩边之谬。至此而归正矣。布帽带麻之误。由是而得当矣。求之先王之制。而莫不吻然。考诸圣人之礼。而无所差了。一洗千古相承之陋习。永垂百世不易之成法。可以增光于前代。可以有辞于后世。呜呼盛矣。其亦可谓无有馀憾者矣。当是时也。大臣之所献议者。非不纤悉矣。该曹之所覆启者。非不详尽矣。而临丧仓卒。举朝悲扰。不遑博考。或欠致详仪注之间。众议纷然。若以议者之言言之。或曰。丧冠之一二梁。非古也。又曰。承衰之服。不可无也。又曰。不论追服而多有窒碍。又曰。儒生之衰不成而无所依据。又曰。祥衰不练。有乖于大功熟布之说。又曰。麻绞变布。不可用公士众臣之礼。又曰。熟麻代葛。甚苟简。又曰。冠缨用布。亦可疑。疑端不一。辨难未已。莫不以邦丧之复古为幸。而犹惜其节文之未备。莫不以大礼之得正为言。而尚嗟其条例之未尽。愚未知 朝家定制。自无差谬。而或人之说。出于苛摘耶。抑未知或人之说。尽有可据。而朝制果有错误者耶。又未知朝制。与或人之说。俱有彼此之得失。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0L 页
 各有折衷而取舍者耶。愚敢忘其固陋僭越而略陈蠡管之一二焉。谨按丧冠之制。仪礼丧服疏曰。其冠三辟积。所谓三辟积。即三梁也。家礼斩衰条曰。冠制为三㡇。所谓三㡇。亦三梁也。第朱子服议。减天子冠二十四梁为十二梁。群臣之冠。当如本品进贤冠之数。此则朱子以三梁为士礼。而不专袭仪礼者也。然以语类所载者见之。所论冠梁之制。自三以上。则尽有五梁七梁之渐加者。而自三以下。则元无一梁二梁之等减者。此则朱子之意。亦以三梁为准也。今日丧冠之一二梁者。本出于五礼仪朝服冠之数。则其非古制者明矣。考之仪礼家礼而差错如此。稽诸服议语类而乖剌如此。孟子曰。如知其非。斯速已矣。惜乎。无以此语提醒于当日宗伯之耳也。谨按承衰之服。仪礼丧服图式所谓深衣是也。虽斩衰。亦以布缘边。尝观语类朱子答叶贺孙之问曰。深衣于古为便服。却于凶服。仿而为之。加衰宜矣。第我国丧礼。以中单衣之制用之。此虽非古之深衣。而盖亦仿其制而承衰者也。若以古礼及朱子说。我国通行之规观之。所谓承衰之服。无论深衣中单衣。而终不可无者也。今日斩衰之制。上下一循。而独于承衰服一款。阙而
各有折衷而取舍者耶。愚敢忘其固陋僭越而略陈蠡管之一二焉。谨按丧冠之制。仪礼丧服疏曰。其冠三辟积。所谓三辟积。即三梁也。家礼斩衰条曰。冠制为三㡇。所谓三㡇。亦三梁也。第朱子服议。减天子冠二十四梁为十二梁。群臣之冠。当如本品进贤冠之数。此则朱子以三梁为士礼。而不专袭仪礼者也。然以语类所载者见之。所论冠梁之制。自三以上。则尽有五梁七梁之渐加者。而自三以下。则元无一梁二梁之等减者。此则朱子之意。亦以三梁为准也。今日丧冠之一二梁者。本出于五礼仪朝服冠之数。则其非古制者明矣。考之仪礼家礼而差错如此。稽诸服议语类而乖剌如此。孟子曰。如知其非。斯速已矣。惜乎。无以此语提醒于当日宗伯之耳也。谨按承衰之服。仪礼丧服图式所谓深衣是也。虽斩衰。亦以布缘边。尝观语类朱子答叶贺孙之问曰。深衣于古为便服。却于凶服。仿而为之。加衰宜矣。第我国丧礼。以中单衣之制用之。此虽非古之深衣。而盖亦仿其制而承衰者也。若以古礼及朱子说。我国通行之规观之。所谓承衰之服。无论深衣中单衣。而终不可无者也。今日斩衰之制。上下一循。而独于承衰服一款。阙而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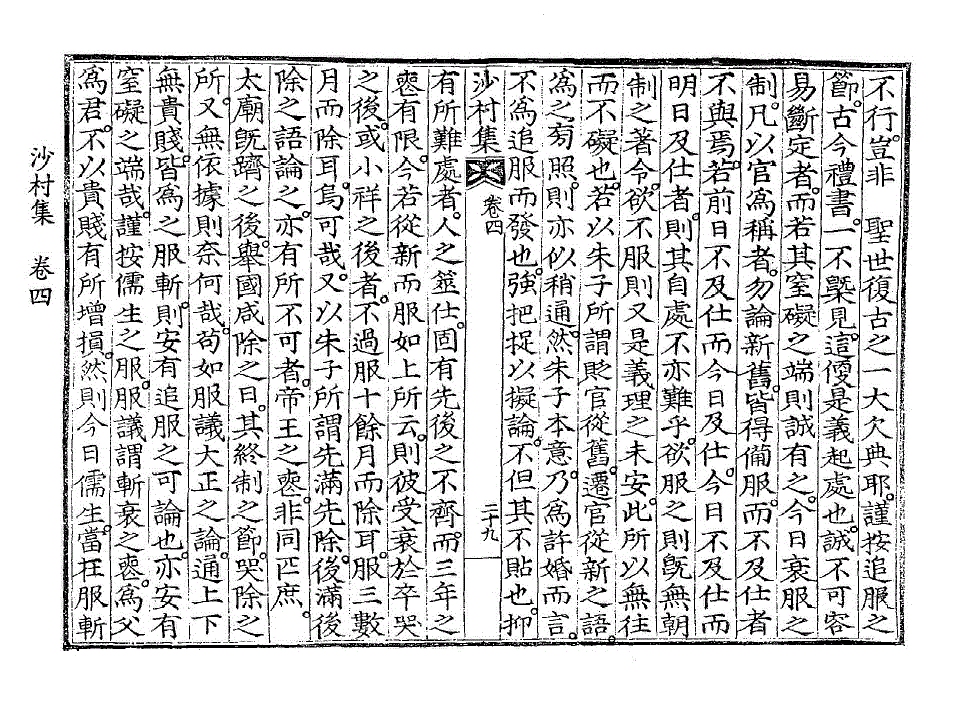 不行。岂非 圣世复古之一大欠典耶。谨按追服之节。古今礼书。一不槩见。这便是义起处也。诚不可容易断定者。而若其窒碍之端则诚有之。今日衰服之制。凡以官为称者。勿论新旧。皆得备服。而不及仕者不与焉。若前日不及仕而今日及仕。今日不及仕而明日及仕者。则其自处不亦难乎。欲服之则既无朝制之著令。欲不服则又是义理之未安。此所以无往而不碍也。若以朱子所谓贬官从旧。迁官从新之语。为之旁照。则亦似稍通。然朱子本意。乃为许婚而言。不为追服而发也。强把捉以拟论。不但其不贴也。抑有所难处者。人之筮仕。固有先后之不齐。而三年之丧有限。今若从新而服如上所云。则彼受衰于卒哭之后。或小祥之后者。不过服十馀月而除耳。服三数月而除耳。乌可哉。又以朱子所谓先满先除。后满后除之语论之。亦有所不可者。帝王之丧。非同匹庶。 太庙既跻之后。举国咸除之日。其终制之节。哭除之所。又无依据则奈何哉。苟如服议大正之论。通上下无贵贱。皆为之服斩。则安有追服之可论也。亦安有窒碍之端哉。谨按儒生之服。服议谓斩衰之丧。为父为君。不以贵贱有所增损。然则今日儒生。当在服斩
不行。岂非 圣世复古之一大欠典耶。谨按追服之节。古今礼书。一不槩见。这便是义起处也。诚不可容易断定者。而若其窒碍之端则诚有之。今日衰服之制。凡以官为称者。勿论新旧。皆得备服。而不及仕者不与焉。若前日不及仕而今日及仕。今日不及仕而明日及仕者。则其自处不亦难乎。欲服之则既无朝制之著令。欲不服则又是义理之未安。此所以无往而不碍也。若以朱子所谓贬官从旧。迁官从新之语。为之旁照。则亦似稍通。然朱子本意。乃为许婚而言。不为追服而发也。强把捉以拟论。不但其不贴也。抑有所难处者。人之筮仕。固有先后之不齐。而三年之丧有限。今若从新而服如上所云。则彼受衰于卒哭之后。或小祥之后者。不过服十馀月而除耳。服三数月而除耳。乌可哉。又以朱子所谓先满先除。后满后除之语论之。亦有所不可者。帝王之丧。非同匹庶。 太庙既跻之后。举国咸除之日。其终制之节。哭除之所。又无依据则奈何哉。苟如服议大正之论。通上下无贵贱。皆为之服斩。则安有追服之可论也。亦安有窒碍之端哉。谨按儒生之服。服议谓斩衰之丧。为父为君。不以贵贱有所增损。然则今日儒生。当在服斩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1L 页
 之列者。断然无疑。顾乃以区区一小麻带。苟然谓之斩衰。考于历代之礼书。而俱无可据。此果成斩衰之服乎。兴居带麻。终守三年者。虽与所谓士庶之齐衰三月者有异。而以首则不见冠绖矣。以身则不用衰裳矣。名为斩衰之丧。而反不若功缌之服。此其所失。较他尤大。而荏苒日月。终未闻变通者。愚敢谓今日之不可不改者此也。谨按祥衰之练。服问疏曰。斩衰既练而服功衰。以大功七升布为衰裳。横渠又曰。练衣必锻鍊大功之布为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斩衰章疏曰。七升以上故灰矣。以此观之。小祥衰衣之并练。恐无可疑。第檀弓云。练衣中衣之承衰者。疏又云正服不变。练祭受服图云。只练中衣及冠。由是言之。衰裳之不练。亦似无妨。然仪礼用布。只言升数。虽缌服之布。亦不言熟。此甚可疑。抑既言七升。则虽不言熟而练在其中之意耶。家礼大功条曰。用稍粗熟布。小祥条曰。设次陈练服。祥后练布。又见于墨衰之问。与上服问疏,横渠说,斩衰章疏等说。俱极分晓。最合受用。且练祭之练。本是练布之练。则今只练冠而不练衰者。其于朱子说。何如也。谨按斩衰布绞。仪礼公士大夫众臣之服也。夫众臣之于公士大夫。压
之列者。断然无疑。顾乃以区区一小麻带。苟然谓之斩衰。考于历代之礼书。而俱无可据。此果成斩衰之服乎。兴居带麻。终守三年者。虽与所谓士庶之齐衰三月者有异。而以首则不见冠绖矣。以身则不用衰裳矣。名为斩衰之丧。而反不若功缌之服。此其所失。较他尤大。而荏苒日月。终未闻变通者。愚敢谓今日之不可不改者此也。谨按祥衰之练。服问疏曰。斩衰既练而服功衰。以大功七升布为衰裳。横渠又曰。练衣必锻鍊大功之布为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斩衰章疏曰。七升以上故灰矣。以此观之。小祥衰衣之并练。恐无可疑。第檀弓云。练衣中衣之承衰者。疏又云正服不变。练祭受服图云。只练中衣及冠。由是言之。衰裳之不练。亦似无妨。然仪礼用布。只言升数。虽缌服之布。亦不言熟。此甚可疑。抑既言七升。则虽不言熟而练在其中之意耶。家礼大功条曰。用稍粗熟布。小祥条曰。设次陈练服。祥后练布。又见于墨衰之问。与上服问疏,横渠说,斩衰章疏等说。俱极分晓。最合受用。且练祭之练。本是练布之练。则今只练冠而不练衰者。其于朱子说。何如也。谨按斩衰布绞。仪礼公士大夫众臣之服也。夫众臣之于公士大夫。压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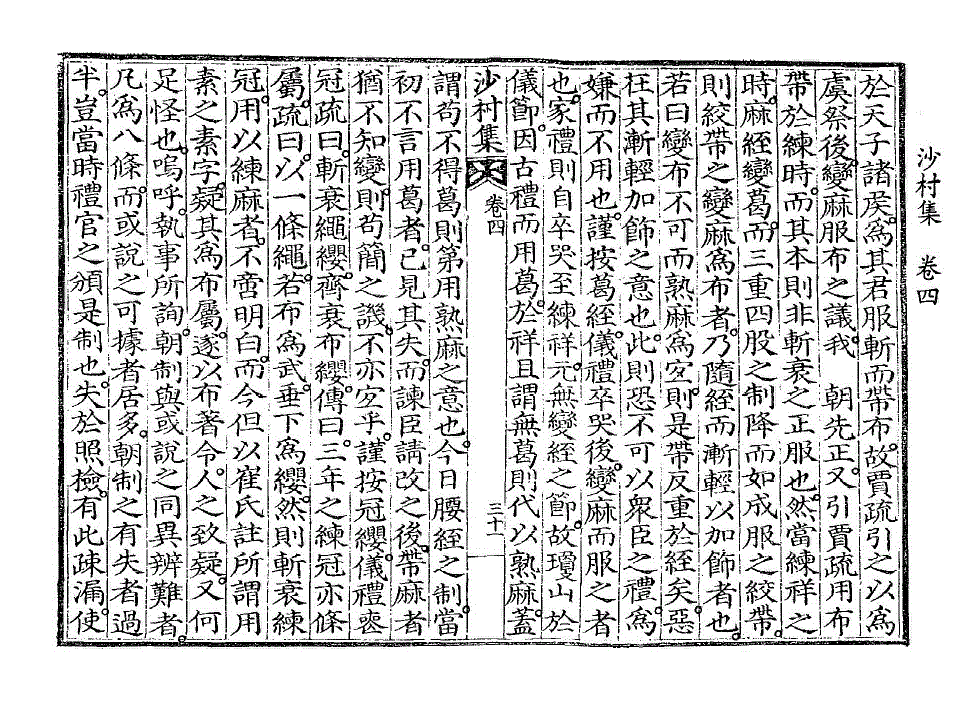 于天子诸侯。为其君服斩而带布。故贾疏引之以为虞祭后。变麻服布之议。我 朝先正。又引贾疏用布带于练时。而其本则非斩衰之正服也。然当练祥之时。麻绖变葛。而三重四股之制降而如成服之绞带。则绞带之变麻为布者。乃随绖而渐轻以加饰者也。若曰变布不可而熟麻为宜。则是带反重于绖矣。恶在其渐轻加饰之意也。此则恐不可以众臣之礼。为嫌而不用也。谨按葛绖。仪礼卒哭后。变麻而服之者也。家礼则自卒哭至练祥。元无变绖之节。故琼山于仪节。因古礼而用葛。于祥且谓无葛则代以熟麻。盖谓苟不得葛则第用熟麻之意也。今日腰绖之制。当初不言用葛者。已见其失。而谏臣请改之后。带麻者犹不知变。则苟简之讥。不亦宜乎。谨按冠缨。仪礼丧冠疏曰。斩衰绳缨。齐衰布缨。传曰。三年之练冠亦条属。疏曰。以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缨。然则斩衰练冠。用以练麻者。不啻明白。而今但以崔氏注所谓用素之素字。疑其为布属。遂以布著令。人之致疑。又何足怪也。呜呼。执事所询。朝制与或说之同异辨难者。凡为八条。而或说之可据者居多。朝制之有失者过半。岂当时礼官之颁是制也。失于照检。有此疏漏。使
于天子诸侯。为其君服斩而带布。故贾疏引之以为虞祭后。变麻服布之议。我 朝先正。又引贾疏用布带于练时。而其本则非斩衰之正服也。然当练祥之时。麻绖变葛。而三重四股之制降而如成服之绞带。则绞带之变麻为布者。乃随绖而渐轻以加饰者也。若曰变布不可而熟麻为宜。则是带反重于绖矣。恶在其渐轻加饰之意也。此则恐不可以众臣之礼。为嫌而不用也。谨按葛绖。仪礼卒哭后。变麻而服之者也。家礼则自卒哭至练祥。元无变绖之节。故琼山于仪节。因古礼而用葛。于祥且谓无葛则代以熟麻。盖谓苟不得葛则第用熟麻之意也。今日腰绖之制。当初不言用葛者。已见其失。而谏臣请改之后。带麻者犹不知变。则苟简之讥。不亦宜乎。谨按冠缨。仪礼丧冠疏曰。斩衰绳缨。齐衰布缨。传曰。三年之练冠亦条属。疏曰。以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缨。然则斩衰练冠。用以练麻者。不啻明白。而今但以崔氏注所谓用素之素字。疑其为布属。遂以布著令。人之致疑。又何足怪也。呜呼。执事所询。朝制与或说之同异辨难者。凡为八条。而或说之可据者居多。朝制之有失者过半。岂当时礼官之颁是制也。失于照检。有此疏漏。使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2L 页
 具眼于礼家者。得以證其得失耶。邦丧服制之议。盖始于甲午矣。自甲午至今日。居然八载。则日月不为不久矣。论讲不为不熟矣。博询于庙堂之宰辅。广问于草野之儒贤。折衷众议。采择用之。宜其引据明白。考證的确。指南一世。行之无疑。而顾今仪节条件。差谬者亦多。则信乎礼疑之无穷至此哉。虽然。星霜荏苒。时序推迁。 成服已矣。练事忽焉。此等节目。惜乎无及。执事之问。愚生之答。亦不过为閒酬酢矣。顾愚生之所欲言者。不在于区区仪注间而已。则请拔脱规例。推本而竭论之。呜呼。为父斩衰。何也。至尊也。为君斩衰。何也。亦至尊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君父之丧。哀痛之心。发于天性。不待勉强。圣人于此。制为斩衰。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在上者。必先摧恸而临之。攀擗以行之。居庐宅宗。自尽孝思。然后群臣观感。四方取则。哀尽于上而莫不致哀。礼循于此而莫不率礼。未有为其子者不哀。而为其臣者能哀也。未有恩之至者不戚。而义以合者能戚也。滕文公之居丧也。四方来观。吊者大悦。夫四方之观者。本非滕之臣庶也。诸侯之吊者。亦非滕之大夫也。其所以心悦诚服。至于如此者。以文公之诚孝发外。而哀陨
具眼于礼家者。得以證其得失耶。邦丧服制之议。盖始于甲午矣。自甲午至今日。居然八载。则日月不为不久矣。论讲不为不熟矣。博询于庙堂之宰辅。广问于草野之儒贤。折衷众议。采择用之。宜其引据明白。考證的确。指南一世。行之无疑。而顾今仪节条件。差谬者亦多。则信乎礼疑之无穷至此哉。虽然。星霜荏苒。时序推迁。 成服已矣。练事忽焉。此等节目。惜乎无及。执事之问。愚生之答。亦不过为閒酬酢矣。顾愚生之所欲言者。不在于区区仪注间而已。则请拔脱规例。推本而竭论之。呜呼。为父斩衰。何也。至尊也。为君斩衰。何也。亦至尊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君父之丧。哀痛之心。发于天性。不待勉强。圣人于此。制为斩衰。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在上者。必先摧恸而临之。攀擗以行之。居庐宅宗。自尽孝思。然后群臣观感。四方取则。哀尽于上而莫不致哀。礼循于此而莫不率礼。未有为其子者不哀。而为其臣者能哀也。未有恩之至者不戚。而义以合者能戚也。滕文公之居丧也。四方来观。吊者大悦。夫四方之观者。本非滕之臣庶也。诸侯之吊者。亦非滕之大夫也。其所以心悦诚服。至于如此者。以文公之诚孝发外。而哀陨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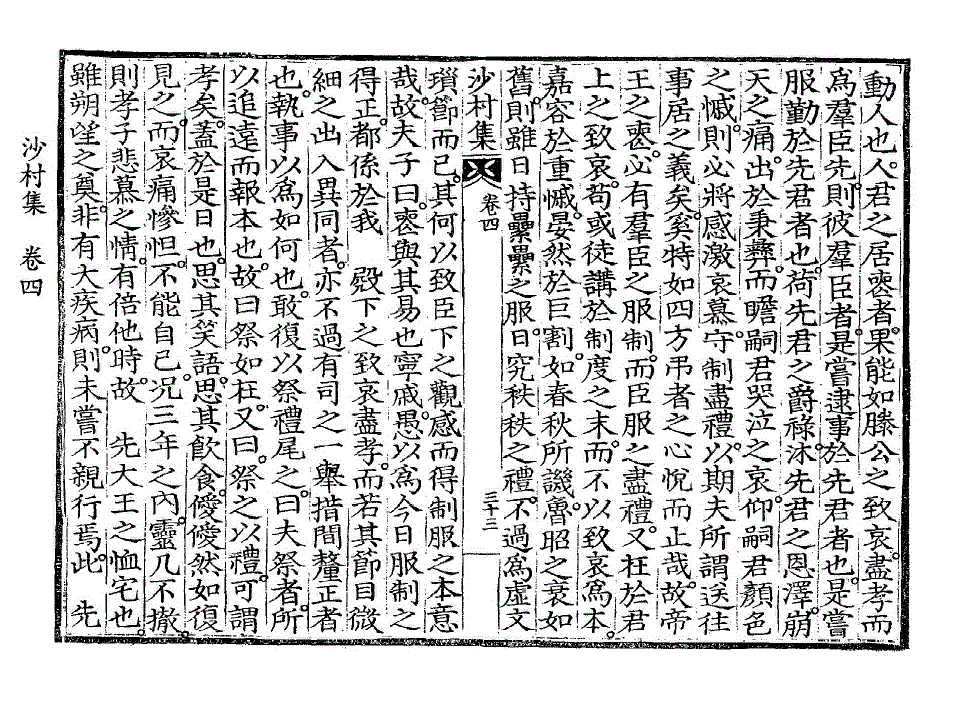 动人也。人君之居丧者。果能如滕公之致哀。尽孝而为群臣先。则彼群臣者。是尝逮事于先君者也。是尝服勤于先君者也。荷先君之爵禄。沐先君之恩泽。崩天之痛。出于秉彝。而瞻嗣君哭泣之哀。仰嗣君颜色之戚。则必将感激哀慕。守制尽礼。以期夫所谓送往事居之义矣。奚特如四方吊者之心悦而止哉。故帝王之丧。必有群臣之服制。而臣服之尽礼。又在于君上之致哀。苟或徒讲于制度之末。而不以致哀为本。嘉容于重戚。晏然于巨割。如春秋所讥。鲁昭之衰如旧。则虽日持累累之服。日究秩秩之礼。不过为虚文琐节而已。其何以致臣下之观感而得制服之本意哉。故夫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愚以为今日服制之得正。都系于我 殿下之致哀尽孝。而若其节目微细之出入异同者。亦不过有司之一举措间釐正者也。执事以为如何也。敢复以祭礼尾之。曰夫祭者。所以追远而报本也。故曰祭如在。又曰。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盖于是日也。思其笑语。思其饮食。僾僾然如复见之。而哀痛惨怛。不能自已。况三年之内。灵几不撤。则孝子悲慕之情。有倍他时。故 先大王之恤宅也。虽朔望之奠。非有大疾病。则未尝不亲行焉。此 先
动人也。人君之居丧者。果能如滕公之致哀。尽孝而为群臣先。则彼群臣者。是尝逮事于先君者也。是尝服勤于先君者也。荷先君之爵禄。沐先君之恩泽。崩天之痛。出于秉彝。而瞻嗣君哭泣之哀。仰嗣君颜色之戚。则必将感激哀慕。守制尽礼。以期夫所谓送往事居之义矣。奚特如四方吊者之心悦而止哉。故帝王之丧。必有群臣之服制。而臣服之尽礼。又在于君上之致哀。苟或徒讲于制度之末。而不以致哀为本。嘉容于重戚。晏然于巨割。如春秋所讥。鲁昭之衰如旧。则虽日持累累之服。日究秩秩之礼。不过为虚文琐节而已。其何以致臣下之观感而得制服之本意哉。故夫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愚以为今日服制之得正。都系于我 殿下之致哀尽孝。而若其节目微细之出入异同者。亦不过有司之一举措间釐正者也。执事以为如何也。敢复以祭礼尾之。曰夫祭者。所以追远而报本也。故曰祭如在。又曰。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盖于是日也。思其笑语。思其饮食。僾僾然如复见之。而哀痛惨怛。不能自已。况三年之内。灵几不撤。则孝子悲慕之情。有倍他时。故 先大王之恤宅也。虽朔望之奠。非有大疾病。则未尝不亲行焉。此 先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3L 页
 大王圣孝之出常万万。而至今舆情钦诵不已者也。愿执事入告 嗣王。聿追 先休。必亲祭奠。以光孝思。次讲礼典。以正服制。则 先大王所以讲定礼制。燕翼后嗣者。至此而更无遗欠矣。噫。霜露既降。节物伤心。仰承明问。百感弸中。追惟 先朝。欲语旋咽。临纸涕泣。不知所云。谨对。
大王圣孝之出常万万。而至今舆情钦诵不已者也。愿执事入告 嗣王。聿追 先休。必亲祭奠。以光孝思。次讲礼典。以正服制。则 先大王所以讲定礼制。燕翼后嗣者。至此而更无遗欠矣。噫。霜露既降。节物伤心。仰承明问。百感弸中。追惟 先朝。欲语旋咽。临纸涕泣。不知所云。谨对。沙村集卷之四
策问
[君子与小人]
问。自古君子与小人。互有进退。而君子常不胜。小人常胜。君子之治小人。常失于宽。小人之治君子。常过于刻。何也。唐虞之际。元凯登庸。共兜流窜。此则可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自是以降。则飞廉恶来之用事。而父师少师之或死或囚。史高恭显之擅朝。而望之堪猛之相继杀死者。何也。东京之三君八俊。或以勋戚大臣。或以正直贤士。当路握权。而俱被节甫之屠戮。汴宋之洛朔诸君子。或以开继大贤。或以顾命元老。得君立朝。而终为惇卞之网打。此或格王正事之道。有所未尽而至此耶。寇莱公决却虏之策。为真宗信任。而非惟不能去钦若。反为所陷。张魏公建平苗之功。为高宗倚仗。而不但不能除秦桧。反被所害。岂亦为国谋事之术有所不臧而致然耶。李林甫之
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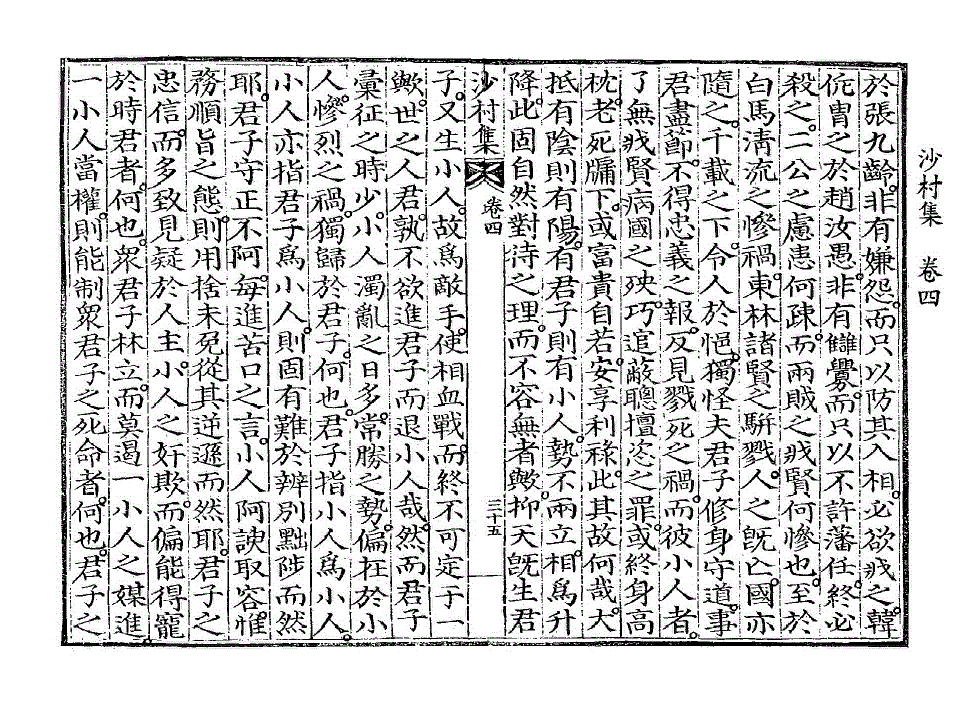 于张九龄。非有嫌怨。而只以防其入相。必欲戕之。韩侂胄之于赵汝愚。非有雠衅。而只以不许藩任。终必杀之。二公之虑患何疏。而两贼之戕贤何惨也。至于白马清流之惨祸。东林诸贤之骈戮。人之既亡。国亦随之。千载之下。令人于悒。独怪夫君子修身守道。事君尽节。不得忠义之报。反见戮死之祸。而彼小人者。了无戕贤病国之殃。巧逭蔽聪擅恣之罪。或终身高枕。老死牖下。或富贵自若。安享利禄。此其故何哉。大抵有阴则有阳。有君子则有小人。势不两立。相为升降。此固自然对待之理。而不容无者欤。抑天既生君子。又生小人。故为敌手。使相血战。而终不可定于一欤。世之人君。孰不欲进君子而退小人哉。然而君子汇征之时少。小人浊乱之日多。常胜之势。偏在于小人。惨烈之祸。独归于君子。何也。君子指小人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则固有难于辨别黜陟而然耶。君子守正不阿。每进苦口之言。小人阿谀取容。惟务顺旨之态。则用舍未免从其逆逊而然耶。君子之忠信。而多致见疑于人主。小人之奸欺。而偏能得宠于时君者。何也。众君子林立。而莫遏一小人之媒进。一小人当权。则能制众君子之死命者。何也。君子之
于张九龄。非有嫌怨。而只以防其入相。必欲戕之。韩侂胄之于赵汝愚。非有雠衅。而只以不许藩任。终必杀之。二公之虑患何疏。而两贼之戕贤何惨也。至于白马清流之惨祸。东林诸贤之骈戮。人之既亡。国亦随之。千载之下。令人于悒。独怪夫君子修身守道。事君尽节。不得忠义之报。反见戮死之祸。而彼小人者。了无戕贤病国之殃。巧逭蔽聪擅恣之罪。或终身高枕。老死牖下。或富贵自若。安享利禄。此其故何哉。大抵有阴则有阳。有君子则有小人。势不两立。相为升降。此固自然对待之理。而不容无者欤。抑天既生君子。又生小人。故为敌手。使相血战。而终不可定于一欤。世之人君。孰不欲进君子而退小人哉。然而君子汇征之时少。小人浊乱之日多。常胜之势。偏在于小人。惨烈之祸。独归于君子。何也。君子指小人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则固有难于辨别黜陟而然耶。君子守正不阿。每进苦口之言。小人阿谀取容。惟务顺旨之态。则用舍未免从其逆逊而然耶。君子之忠信。而多致见疑于人主。小人之奸欺。而偏能得宠于时君者。何也。众君子林立。而莫遏一小人之媒进。一小人当权。则能制众君子之死命者。何也。君子之沙村集卷之四 第 334L 页
 进也。正谊不谋其利。明道不计其功。及其退也。守分俟命。非义不为。小人之进也。持禄保位。非不足矣。而必以杀君子为事。至其不可遍除。则必假朋党之目。谋逆之名。荧惑主听。尽杀乃已。及其退也。缔谋并力。窥觊复入。因缘幽阴。百道攻钻。而其排布设施之计。尽多有奇秘者。岂君子忠厚公直有馀。而坚忍刚猛。谋虑计策。不及于小人而然耶。以我东言之。自罗迄丽。中间治乱。皆系君子小人之用舍。则其详可历指欤。于休 国朝。治埒姚姒。贤能得舆。俊杰登朝。固无所谓小人浊乱之忧。然而己卯乙巳之祸。惨毒酷烈。先儒至谓足以亡国。至今士论冤痛不已。 仁 明之际。圣明相继。而仅复静庵之官。只削元衡之爵。终无以大慰诸贤冤郁之魂。快正群奸屠杀之罪者。何也。继此以后。则更无所谓小人戕君子之祸耶。何以则内君子外小人。致休明之治而无孽牙之患耶。诸生必有明于阴阳淑慝之分者。其各悉陈。
进也。正谊不谋其利。明道不计其功。及其退也。守分俟命。非义不为。小人之进也。持禄保位。非不足矣。而必以杀君子为事。至其不可遍除。则必假朋党之目。谋逆之名。荧惑主听。尽杀乃已。及其退也。缔谋并力。窥觊复入。因缘幽阴。百道攻钻。而其排布设施之计。尽多有奇秘者。岂君子忠厚公直有馀。而坚忍刚猛。谋虑计策。不及于小人而然耶。以我东言之。自罗迄丽。中间治乱。皆系君子小人之用舍。则其详可历指欤。于休 国朝。治埒姚姒。贤能得舆。俊杰登朝。固无所谓小人浊乱之忧。然而己卯乙巳之祸。惨毒酷烈。先儒至谓足以亡国。至今士论冤痛不已。 仁 明之际。圣明相继。而仅复静庵之官。只削元衡之爵。终无以大慰诸贤冤郁之魂。快正群奸屠杀之罪者。何也。继此以后。则更无所谓小人戕君子之祸耶。何以则内君子外小人。致休明之治而无孽牙之患耶。诸生必有明于阴阳淑慝之分者。其各悉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