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黄皋集卷之六 第 x 页
黄皋集卷之六
哀辞
哀辞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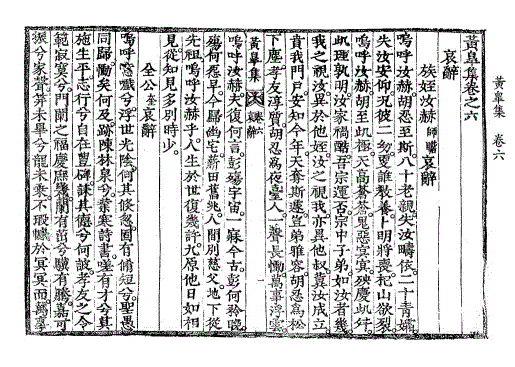 族侄汝赫(师瞻)哀辞
族侄汝赫(师瞻)哀辞呜呼汝赫。胡忍至斯。八十老亲。失汝畴依。二十青孀。失汝安仰。况彼二幼。更谁教养。卜明将丧。杞山欲裂。呜呼汝赫。胡至此极。天高苍苍。鬼恶冥冥。殃庆此舛。此理孰明。汝家祸酷。吾宗运否。宗中子弟。如汝者几。我之视汝。异于他侄。汝之视我。亦异他叔。冀汝成立。贲我门户。安知今年。天夺斯遽。岂弟雅容。胡忍为松下尘。孝友淳质。胡忍为夜台人。一声长恸。万事浮云。呜呼汝赫。夫复何言。彭殇宇宙。一寐今古。彭何矜晚。殇何怨早。今归幽宅。薪田旧兆。人间别慈父。地下从先祖。呜呼汝赫乎。人生于世复几许。九原他日如相见。从知见多别时少。
全公(奎)哀辞
呜呼噫嚱兮。浮世光阴。何其倏忽。固有脩短兮。圣愚同归。恸矣何及。迹陈林泉兮。业寒诗书。嗟有才兮莫施生平。志行兮自在礼碑。诔其德兮何诐。孝友之令范寂寞兮。门阑之福庆庶几。兰有茁兮骥有腾。嘉可振兮家声。笄未毕兮龙未乘。不瑕憾于冥冥而。万事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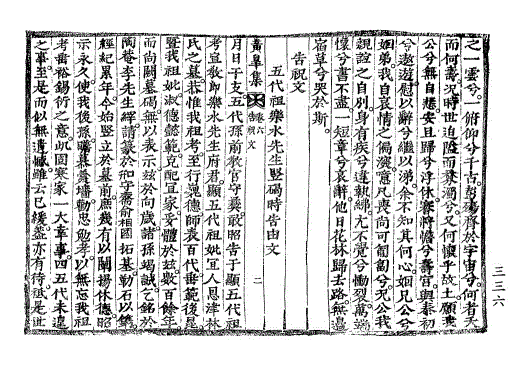 之一云兮。一俯仰兮千古。彭殇齐于宇宙兮。何者夭而何寿。况时世迫隘而棼浊兮。又何怀乎故土。愿我公兮无自悲。安且归兮浮休。謇将憺兮寿宫。与泰初兮遨游。慰以辞兮继以涕。余不知其何心。姻兄公兮姻弟。我自哀情之偏深。噫凡丧尚可匍匐兮。况公我亲谊之自别。身有疾兮违执绋。尤不觉兮恸裂。万端怀兮书不尽。一短章兮哀辞。他日花林归去路。无边宿草兮哭于斯。
之一云兮。一俯仰兮千古。彭殇齐于宇宙兮。何者夭而何寿。况时世迫隘而棼浊兮。又何怀乎故土。愿我公兮无自悲。安且归兮浮休。謇将憺兮寿宫。与泰初兮遨游。慰以辞兮继以涕。余不知其何心。姻兄公兮姻弟。我自哀情之偏深。噫凡丧尚可匍匐兮。况公我亲谊之自别。身有疾兮违执绋。尤不觉兮恸裂。万端怀兮书不尽。一短章兮哀辞。他日花林归去路。无边宿草兮哭于斯。黄皋集卷之六
告祝文
五代祖乐水先生竖碣时告由文
月日干支。五代孙前教官守彝。敢昭告于显五代祖考宣教郎乐水先生府君。显五代祖妣宜人恩津林氏之墓。恭惟我祖考。至行巍德。师表百代。垂范后昆。暨我祖妣。淑德懿范。克配宜家。妥体于玆。数百馀年。而尚阙墓碣。无以表示。玆于向岁。诸孙竭诚。乞铭于陶庵李先生縡。请篆于知守斋俞相国拓基。勒石以镌。经纪累年。今始竖立于墓前。庶几有以阐扬休德。昭示永久。使我后孙。瞻慕羹墙。劝忠勉孝。以无忘我祖考垂裕锡衍之意。此固寒家一大幸事。四五代未遑之事。至是而似无遗憾。虽云已缓。盖亦有待。祗是世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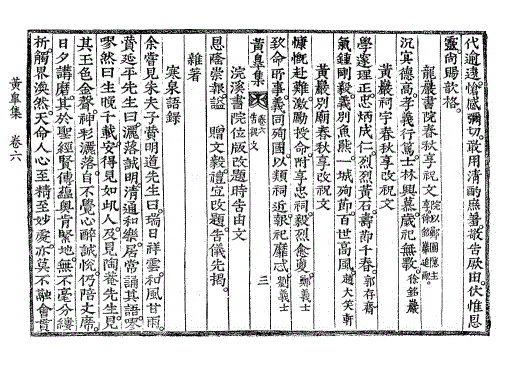 代逾远。怆感弥切。敢用清酌庶羞。敬告厥由。伏惟恩灵。尚赐歆格。
代逾远。怆感弥切。敢用清酌庶羞。敬告厥由。伏惟恩灵。尚赐歆格。龙岩书院春秋享祝文(院以郑圃隐主享。徐铭岩追配。)
沉冥德高。孝义行笃。士林兴慕。岁祀无斁。(徐铭岩)
黄岩祠宇春秋享改祝文
学邃理正。忠炳成仁。烈烈黄石。寿节千春。(郭存斋)
气钟刚毅。义别鱼熊。一城殉节。百世高风。(赵大笑轩)
黄岩别庙春秋享改祝文
慷慨赴难。激励授命。附享忠祠。毅烈愈夐。(郑义士)
致命所事。义同殉国。以类祠近。报祀靡忒。(刘义士)
浣溪书院位版改题时告由文
恩隆崇报。谥 赠文毅。礼宜改题。告仪先揭。
黄皋集卷之六
杂著
寒泉语录
余尝见朱夫子赞明道先生曰。瑞日祥云。和风甘雨。赞延平先生曰。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居常诵其语。嘐嘐然曰生晚千载。安得见如此人。及见陶庵先生。见其玉色金声。神彩洒落。自不觉心醉诚悦。仍陪丈席。日夕讲磨。其于圣经贤传蕴奥肯紧地。无不毫分缕析。触界涣然。天命人心至精至妙处。亦莫不融会贯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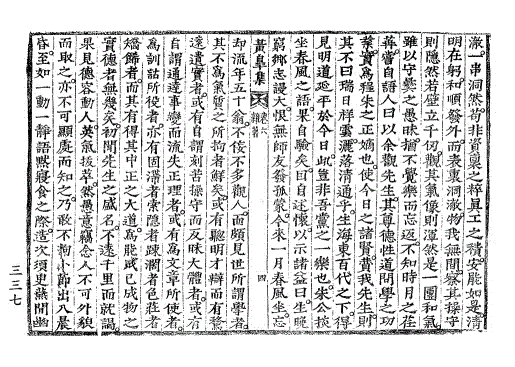 澈。一串洞然。苟非资禀之粹真工之积。安能如是。清明在躬。和顺发外。而表里洞澈。物我无间。察其操守则隐然若壁立千仞。观其气像则浑然是一团和气。虽以守彝之愚昧。犹不觉乐而忘返。不知时月之荏苒。尝自语人曰以余观先生。其尊德性道问学之功业。实为程朱之正嫡也。使今日之诸贤。赞我先生。则其不曰瑞日祥云。洒落清通乎。生海东百代之下。得见明道延平于今日。此岂非吾党之一乐也。朱公掞坐春风之语。果自验矣。因自述怀。以示诸益曰。生晚穷乡志谩大。恨无师友发孤蒙。今来一月春风坐。忘却流年五十翁。不佞不多观人。而颇见世所谓学者。其不为气质之所拘者鲜矣。或有聪明才辩而有骛远遗实者。或有自谓刻苦操守而反昧大体者。或有自谓通达事变而流失正理者。或有为文章所使者。为训诂所役者。亦有固滞者索隐者疏阔者色庄者矫饰者。而其有得其中正之大道。为能成己成物之实德者无几矣。初闻先生之盛名。不远千里而就谒。果见德容动人。英气拔萃。然愚意窃念人不可外貌而取之。亦不可显处而知之。乃敢不拘小节出入晨昏。至如一动一静语默寝食之际。造次须臾燕閒幽
澈。一串洞然。苟非资禀之粹真工之积。安能如是。清明在躬。和顺发外。而表里洞澈。物我无间。察其操守则隐然若壁立千仞。观其气像则浑然是一团和气。虽以守彝之愚昧。犹不觉乐而忘返。不知时月之荏苒。尝自语人曰以余观先生。其尊德性道问学之功业。实为程朱之正嫡也。使今日之诸贤。赞我先生。则其不曰瑞日祥云。洒落清通乎。生海东百代之下。得见明道延平于今日。此岂非吾党之一乐也。朱公掞坐春风之语。果自验矣。因自述怀。以示诸益曰。生晚穷乡志谩大。恨无师友发孤蒙。今来一月春风坐。忘却流年五十翁。不佞不多观人。而颇见世所谓学者。其不为气质之所拘者鲜矣。或有聪明才辩而有骛远遗实者。或有自谓刻苦操守而反昧大体者。或有自谓通达事变而流失正理者。或有为文章所使者。为训诂所役者。亦有固滞者索隐者疏阔者色庄者矫饰者。而其有得其中正之大道。为能成己成物之实德者无几矣。初闻先生之盛名。不远千里而就谒。果见德容动人。英气拔萃。然愚意窃念人不可外貌而取之。亦不可显处而知之。乃敢不拘小节出入晨昏。至如一动一静语默寝食之际。造次须臾燕閒幽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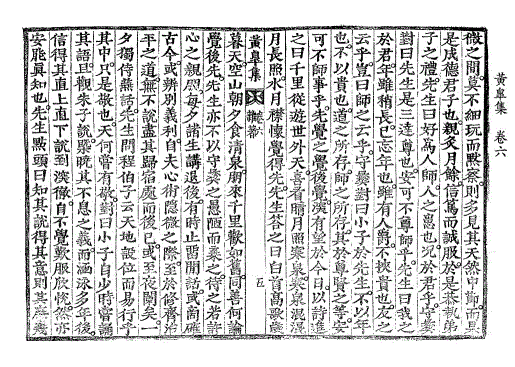 微之间。莫不细玩而默察。则多见其天然中节。而果是成德君子也。亲炙月馀。信笃而诚服。于是恭执弟子之礼。先生曰好为人师。人之患也。况于君乎。守彝对曰先生是三达尊也。安可不尊师乎。先生曰我之于君。年虽稍长。已忘年也。虽有人爵。不挟贵也。友之云乎。岂曰师之云乎。守彝对曰小子于先生。不以年也。不以贵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于尊贤之等。安可不师事乎。先觉之觉后觉。深有望于今日。以诗进之曰千里从游世外天。喜看晴月照寒泉。寒泉混混月长照。水月襟怀觉得先。先生答之曰白首高歌岁暮天。空山朝夕食清泉。朋来千里欢如旧。同善何论觉后先。先生亦不以守彝之愚陋而弃之。待之若许心之亲朋。每夕诸生讲退后。有时止留閒话。或商确古今。或辨别义利。自夫心术隐微之际。至于修齐治平之道。无不说尽其归宿处而后已。或至夜阑矣。一夕独侍燕话。先生问程伯子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天何尝有敬。对曰小子自少时尝诵其语。且观朱子说。槩晓其不息之义。而涵泳多年后。信得其直上直下说到深彻。自不觉叹服欣悦。然亦安能真知也。先生点头曰知其说得其意则其庶几
微之间。莫不细玩而默察。则多见其天然中节。而果是成德君子也。亲炙月馀。信笃而诚服。于是恭执弟子之礼。先生曰好为人师。人之患也。况于君乎。守彝对曰先生是三达尊也。安可不尊师乎。先生曰我之于君。年虽稍长。已忘年也。虽有人爵。不挟贵也。友之云乎。岂曰师之云乎。守彝对曰小子于先生。不以年也。不以贵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于尊贤之等。安可不师事乎。先觉之觉后觉。深有望于今日。以诗进之曰千里从游世外天。喜看晴月照寒泉。寒泉混混月长照。水月襟怀觉得先。先生答之曰白首高歌岁暮天。空山朝夕食清泉。朋来千里欢如旧。同善何论觉后先。先生亦不以守彝之愚陋而弃之。待之若许心之亲朋。每夕诸生讲退后。有时止留閒话。或商确古今。或辨别义利。自夫心术隐微之际。至于修齐治平之道。无不说尽其归宿处而后已。或至夜阑矣。一夕独侍燕话。先生问程伯子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天何尝有敬。对曰小子自少时尝诵其语。且观朱子说。槩晓其不息之义。而涵泳多年后。信得其直上直下说到深彻。自不觉叹服欣悦。然亦安能真知也。先生点头曰知其说得其意则其庶几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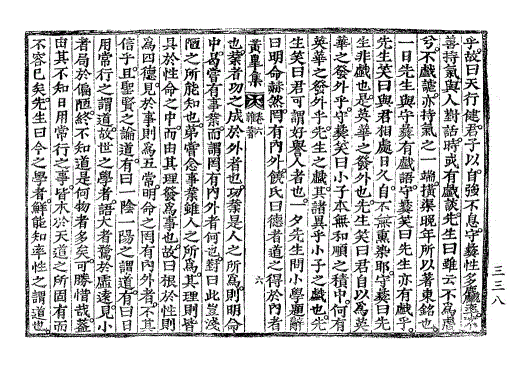 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守彝性多粗率。不善持气。与人对话。时或有戏谈。先生曰虽云不为虐兮。不戏谑。亦持气之一端。横渠晚年所以著东铭也。一日先生与守彝有戏语。守彝笑曰先生亦有戏乎。先生笑曰与君相处日久。自不无熏染耶。守彝曰先生非戏也。是英华之发外也。先生笑曰君自以为英华之发外乎。守彝笑曰小子本无和顺之积中。何有英华之发外乎。先生之戏。其诸异乎小子之戏也。先生笑曰君可谓好誉人者也。一夕先生问小学题辞曰明命赫然。罔有内外。饶氏曰德者道之得于内者也。业者功之成于外者也。功业是人之所为。则明命中。曷尝有事业。而谓罔有内外者何也。对曰此岂浅陋之所能知也。第尝念事业虽人之所为。其理则皆具于性命之中。而由其理发为事也。故曰根于性则为四德。见于事则为五常。明命之罔有内外者。不其信乎。且圣贤之论道。有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曰日用常行之谓道。故世之学者。语大者骛于虚远。见小者局于偏陋。终不知道是何物者多矣。可胜惜哉。盖由其不知日用常行之事。皆木(一作本)于天道之所固有而不容已矣。先生曰今之学者。鲜能知率性之谓道也。
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守彝性多粗率。不善持气。与人对话。时或有戏谈。先生曰虽云不为虐兮。不戏谑。亦持气之一端。横渠晚年所以著东铭也。一日先生与守彝有戏语。守彝笑曰先生亦有戏乎。先生笑曰与君相处日久。自不无熏染耶。守彝曰先生非戏也。是英华之发外也。先生笑曰君自以为英华之发外乎。守彝笑曰小子本无和顺之积中。何有英华之发外乎。先生之戏。其诸异乎小子之戏也。先生笑曰君可谓好誉人者也。一夕先生问小学题辞曰明命赫然。罔有内外。饶氏曰德者道之得于内者也。业者功之成于外者也。功业是人之所为。则明命中。曷尝有事业。而谓罔有内外者何也。对曰此岂浅陋之所能知也。第尝念事业虽人之所为。其理则皆具于性命之中。而由其理发为事也。故曰根于性则为四德。见于事则为五常。明命之罔有内外者。不其信乎。且圣贤之论道。有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曰日用常行之谓道。故世之学者。语大者骛于虚远。见小者局于偏陋。终不知道是何物者多矣。可胜惜哉。盖由其不知日用常行之事。皆木(一作本)于天道之所固有而不容已矣。先生曰今之学者。鲜能知率性之谓道也。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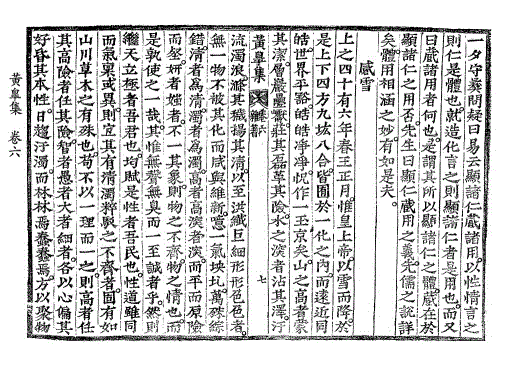 一夕守彝问疑曰易云显诸仁藏诸用。以性情言之则仁是体也。就造化言之则显诸仁者是用也。而又曰藏诸用者何也。是谓其所以显诸仁之体。藏在于显诸仁之用否。先生曰显仁藏用之义。先儒之说详矣。体用相涵之妙。有如是夫。
一夕守彝问疑曰易云显诸仁藏诸用。以性情言之则仁是体也。就造化言之则显诸仁者是用也。而又曰藏诸用者何也。是谓其所以显诸仁之体。藏在于显诸仁之用否。先生曰显仁藏用之义。先儒之说详矣。体用相涵之妙。有如是夫。感雪
上之四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惟皇上帝。以雪而降。于是上下四方九𡉞八合。皆囿于一化之内。而远近同皓。世界平豁。皓皓净净。恍作一玉京矣。山之高者蒙其洁。层岩叠巘。庄其磊革其险。水之深者沾其泽。污流浊浪。涤其秽扬其清。以至洪纤巨细形形色色者。无一物不被其化而咸与维新。噫一气坱圠。万殊综错。清者为清。浊者为浊。高者高深者深。而平而原险而壑。妍者媸者。不一其象。则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而是孰使之一哉。其惟无声无臭而一至诚者乎。然则继天立极者吾君也。均赋是性者吾民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则宜其有清浊粹驳之不齐者。固有如山川草木之有殊也。苟不以一理而一之。则高者任其高险者任其险。智者愚者大者细者。各以心偏其好昏其本性。日趋污浊。而林林焉蠢蠢焉。方以聚物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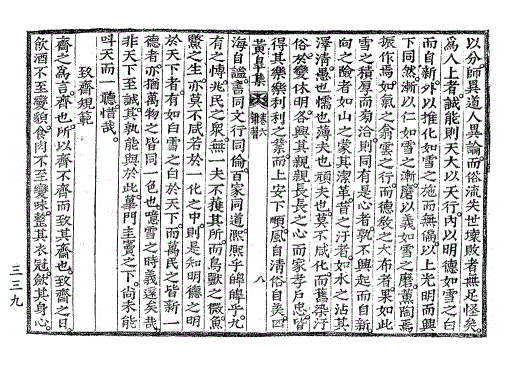 以分。师异道人异论。而俗流失世坏败者无足怪矣。为人上者。诚能则天大以天行。内以明德如雪之白而自新。外以推化如雪之施而无偏。以上光明而兴下同然。渐以仁如雪之渐。磨以义如雪之磨。薰陶焉振作焉。如气之翕云之行。而德教之大布者。果如此雪之积厚而旁洽。则同有是心者。孰不兴起而自新。向之险者如山之蒙其洁革。昔之污者。如水之沾其泽清。愚也懦也薄夫也顽夫也。莫不咸化。而旧染污俗。于变休明。各兴其亲亲长长之心而家孝户忠。皆得其乐乐利利之业。而上安下顺。风自清俗自美。四海自谧。书同文行同伦。百家同道。熙熙乎皞皞乎。九有之博。兆民之众。无一夫不获其所。而鸟兽之微。鱼鳖之生。亦莫不咸若于一化之中。则是知明德之明于天下者。有如白雪之白于天下。而万民之皆新一德者。亦犹万物之皆同一色也。噫雪之时义远矣哉。非天下至诚。其孰能与于此。荜门圭窦之下。尚未能叫天而一听。惜哉。
以分。师异道人异论。而俗流失世坏败者无足怪矣。为人上者。诚能则天大以天行。内以明德如雪之白而自新。外以推化如雪之施而无偏。以上光明而兴下同然。渐以仁如雪之渐。磨以义如雪之磨。薰陶焉振作焉。如气之翕云之行。而德教之大布者。果如此雪之积厚而旁洽。则同有是心者。孰不兴起而自新。向之险者如山之蒙其洁革。昔之污者。如水之沾其泽清。愚也懦也薄夫也顽夫也。莫不咸化。而旧染污俗。于变休明。各兴其亲亲长长之心而家孝户忠。皆得其乐乐利利之业。而上安下顺。风自清俗自美。四海自谧。书同文行同伦。百家同道。熙熙乎皞皞乎。九有之博。兆民之众。无一夫不获其所。而鸟兽之微。鱼鳖之生。亦莫不咸若于一化之中。则是知明德之明于天下者。有如白雪之白于天下。而万民之皆新一德者。亦犹万物之皆同一色也。噫雪之时义远矣哉。非天下至诚。其孰能与于此。荜门圭窦之下。尚未能叫天而一听。惜哉。致斋规范
斋之为言。齐也。所以齐不齐而致其斋也。致斋之日。饮酒不至变貌。食肉不至变味。整其衣冠。敛其身心。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0H 页
 不戏谑不喧哗不乱坐不旷座。庄肃诚一。常若对越。各思其所当执事之规模节次。以至于荐享之时。益加敬谨。无或失礼。大凡怠惰放肆。无礼无义。在家尚不可。况于公堂礼法之地乎。平时尚且不敢。况于祭享致斋之日乎。近世以来。学校教衰。纪纲颓弛。为士者亦或有不省学校所设之本意。不顾礼义所先之重地。至如致斋之时。亦且无所敬谨。徒有服儒服冠儒冠致儒之养。而其为谑浪放肆无所忌惮则反有甚于粗率之武夫。而为长者既无以禁戒。为少者亦不能规责。自少至长。习以为常。于校于院。随处同然。至谓学宫古亦如此。某长亦复如此。承讹袭谬。恬不为耻。至使礼义所出之地。反作放荡游衍之所。世道之寒心。可胜痛哉。自今以后。或有蔑礼自肆者。一告而不听则面责。再告不听黜座。三告不听黜斋。以为规警之地幸甚。
不戏谑不喧哗不乱坐不旷座。庄肃诚一。常若对越。各思其所当执事之规模节次。以至于荐享之时。益加敬谨。无或失礼。大凡怠惰放肆。无礼无义。在家尚不可。况于公堂礼法之地乎。平时尚且不敢。况于祭享致斋之日乎。近世以来。学校教衰。纪纲颓弛。为士者亦或有不省学校所设之本意。不顾礼义所先之重地。至如致斋之时。亦且无所敬谨。徒有服儒服冠儒冠致儒之养。而其为谑浪放肆无所忌惮则反有甚于粗率之武夫。而为长者既无以禁戒。为少者亦不能规责。自少至长。习以为常。于校于院。随处同然。至谓学宫古亦如此。某长亦复如此。承讹袭谬。恬不为耻。至使礼义所出之地。反作放荡游衍之所。世道之寒心。可胜痛哉。自今以后。或有蔑礼自肆者。一告而不听则面责。再告不听黜座。三告不听黜斋。以为规警之地幸甚。慎孝子传
公州儒城县。有世称三省堂慎孝子者。名惟天字道源。居昌人。丽朝左仆射恭献公讳修之远裔。而我 成庙朝名臣讳自建之七代孙也。其后有兰仝有德龄有宗孝有好敏。世袭簪冕。好敏生都总都事逖。都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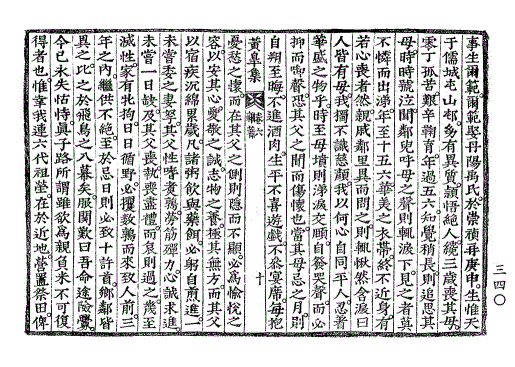 事生尔范。尔范娶丹阳禹氏。于崇祯再庚申。生惟天于儒城屯山村。𢆲有异质。颖悟绝人。才三岁丧其母。零丁孤苦。艰辛鞠育。年过五六。知觉稍长。则追思其母。时时号泣。闻邻儿呼母之声则辄泪下。见之者莫不怜而出涕。年至十五六。华美之衣带。终不近身。有若心丧者然。亲戚邻里异而问之。则辄愀然含泪曰人皆有母。我独不识慈颜。我以何心自同平人。忍着华盛之物乎。时至母坟则涕泪交颐。自发哭声。而必抑而衔声。恐其父之闻而伤怀也。当其母忌之月。则自朔至晦。不进酒肉。生平不喜游戏。不参宴席。每抱忧愁之怀。而在其父之侧则隐而不显。必为愉悦之容。以安其心。爱敬之诚。志物之养。极其无方。而其父以宿疾沉绵累岁。凡诸粥饮与药饵。必躬自煎进。一未尝委之妻孥。其父性嗜煮鹑。劳筋殚力。心诚求进。未尝一日缺。及其父丧。执丧尽礼。而哀则过之。几至灭性。家有牝狗。日日循野。必攫数鹑而来致人前。三年之内。继供不绝。至于忌日则必致十许首。乡邻皆异之。比之于飞鸟之入幕矣。服关(一作阕)叹曰吾命途险衅。今已永失怙恃。真子路所谓虽欲为亲负米不可复得者也。惟幸我连六代祖茔。在于近地。营置祭田。俾
事生尔范。尔范娶丹阳禹氏。于崇祯再庚申。生惟天于儒城屯山村。𢆲有异质。颖悟绝人。才三岁丧其母。零丁孤苦。艰辛鞠育。年过五六。知觉稍长。则追思其母。时时号泣。闻邻儿呼母之声则辄泪下。见之者莫不怜而出涕。年至十五六。华美之衣带。终不近身。有若心丧者然。亲戚邻里异而问之。则辄愀然含泪曰人皆有母。我独不识慈颜。我以何心自同平人。忍着华盛之物乎。时至母坟则涕泪交颐。自发哭声。而必抑而衔声。恐其父之闻而伤怀也。当其母忌之月。则自朔至晦。不进酒肉。生平不喜游戏。不参宴席。每抱忧愁之怀。而在其父之侧则隐而不显。必为愉悦之容。以安其心。爱敬之诚。志物之养。极其无方。而其父以宿疾沉绵累岁。凡诸粥饮与药饵。必躬自煎进。一未尝委之妻孥。其父性嗜煮鹑。劳筋殚力。心诚求进。未尝一日缺。及其父丧。执丧尽礼。而哀则过之。几至灭性。家有牝狗。日日循野。必攫数鹑而来致人前。三年之内。继供不绝。至于忌日则必致十许首。乡邻皆异之。比之于飞鸟之入幕矣。服关(一作阕)叹曰吾命途险衅。今已永失怙恃。真子路所谓虽欲为亲负米不可复得者也。惟幸我连六代祖茔。在于近地。营置祭田。俾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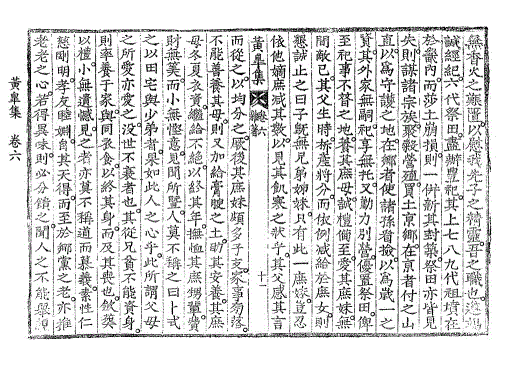 无香火之艰匮。以慰我先子之精灵。吾之职也。遂竭诚经纪。六代祭田。尽办礼祀。其上七八九代祖坟在于畿内。而莎土崩损。则一并新其封筑。祭田亦皆见失。则谋诸宗族。聚谷营殖。买土京乡。在京者付之山直。以为守护之地。在乡者使诸孙看捡。以为岁一之资。其外家无嗣。祀享无托。又勤力别营。优置祭田。俾至祀事不替之地。养其庶母。诚礼备至。爱其庶妹。无间敌己。其父生时。析产将分。而依例减给于庶女。则恳诚止之曰子既无兄弟姊妹。只有此一庶妹。岂忍依他嫡庶减其数。以见其饥寒之状乎。其父感其言而从之。以均分之。厥后其庶妹颇多子支。家事旁落。不能善养其母。则又加给膏腴之土。助其安养。其庶母冬夏衣资。继给不绝。以终其年。抚恤其庶甥辈。费财无算。而小无悭意。见闻所暨。人莫不称之曰卜式之以田宅与少弟者。果如此人之心乎。此所谓父母之所爱亦爱之。没世不衰者也。其从兄贫不能资身。则率养于家。与同衣食。以终其身。而及其丧也。敛葬以礼。小无遗憾。见之者亦莫不称道而慕义。素性仁慈刚明。孝友睦姻。自其天得。而至于乡党之老。亦推老老之心。若得异味。则必分馈之。闻人之不能举亲
无香火之艰匮。以慰我先子之精灵。吾之职也。遂竭诚经纪。六代祭田。尽办礼祀。其上七八九代祖坟在于畿内。而莎土崩损。则一并新其封筑。祭田亦皆见失。则谋诸宗族。聚谷营殖。买土京乡。在京者付之山直。以为守护之地。在乡者使诸孙看捡。以为岁一之资。其外家无嗣。祀享无托。又勤力别营。优置祭田。俾至祀事不替之地。养其庶母。诚礼备至。爱其庶妹。无间敌己。其父生时。析产将分。而依例减给于庶女。则恳诚止之曰子既无兄弟姊妹。只有此一庶妹。岂忍依他嫡庶减其数。以见其饥寒之状乎。其父感其言而从之。以均分之。厥后其庶妹颇多子支。家事旁落。不能善养其母。则又加给膏腴之土。助其安养。其庶母冬夏衣资。继给不绝。以终其年。抚恤其庶甥辈。费财无算。而小无悭意。见闻所暨。人莫不称之曰卜式之以田宅与少弟者。果如此人之心乎。此所谓父母之所爱亦爱之。没世不衰者也。其从兄贫不能资身。则率养于家。与同衣食。以终其身。而及其丧也。敛葬以礼。小无遗憾。见之者亦莫不称道而慕义。素性仁慈刚明。孝友睦姻。自其天得。而至于乡党之老。亦推老老之心。若得异味。则必分馈之。闻人之不能举亲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1L 页
 丧。则必竭力而尽其匍匐之义。凶荒之岁。生计甚艰。而穷族邻里。分赒若己。亦不忍饿莩之遍于道路。日饬家丁。必使稿敛深埋。接人以恭。待人以情。虽微贱寒乞儿。无不矜恻应济。各有条理。见人急难则必挺身以救之。虽至常汉贱隶之死而难收者。或脱衣或给财。俾不为乌鸢食者甚多。闻亲朋之丧则必恸哭而食素累日。贫人之来求财谷。则虽家垂匮乏之时。必为之酬应。故或有不忍发口而自止者。家业不甚礼富。而大小发用。如是夥然。家眷亦不甚冻馁。人皆曰天监所佑。而盖以其通明事理。善为规画。用天道因地利。去奢华节制度故也。其言曰人若贪财汩利牿丧义理者。是禽是兽。而又其昏惰疏迂。不为制产。不能其仰事俯育奉祭接宾者。亦非人道也云。生平为文而终不观科。亲知或劝之。则曰我不习举子之文。虽观科幸中。将何颜行于世乎。执言虽如此。而只以其不识母颜。衔恤隐痛。无与人行世之况也。或临美膳则必太息而涕零。自同罪废。不肯出入。居常默祷曰天只仪容。梦里一见。则可以少泄一生哀慕之情云。而荏苒之间。岁值壬戌。即其母丧重回之年也。其除夕之夜。忽做一梦。慈颜依稀。急进攀裾。自发号
丧。则必竭力而尽其匍匐之义。凶荒之岁。生计甚艰。而穷族邻里。分赒若己。亦不忍饿莩之遍于道路。日饬家丁。必使稿敛深埋。接人以恭。待人以情。虽微贱寒乞儿。无不矜恻应济。各有条理。见人急难则必挺身以救之。虽至常汉贱隶之死而难收者。或脱衣或给财。俾不为乌鸢食者甚多。闻亲朋之丧则必恸哭而食素累日。贫人之来求财谷。则虽家垂匮乏之时。必为之酬应。故或有不忍发口而自止者。家业不甚礼富。而大小发用。如是夥然。家眷亦不甚冻馁。人皆曰天监所佑。而盖以其通明事理。善为规画。用天道因地利。去奢华节制度故也。其言曰人若贪财汩利牿丧义理者。是禽是兽。而又其昏惰疏迂。不为制产。不能其仰事俯育奉祭接宾者。亦非人道也云。生平为文而终不观科。亲知或劝之。则曰我不习举子之文。虽观科幸中。将何颜行于世乎。执言虽如此。而只以其不识母颜。衔恤隐痛。无与人行世之况也。或临美膳则必太息而涕零。自同罪废。不肯出入。居常默祷曰天只仪容。梦里一见。则可以少泄一生哀慕之情云。而荏苒之间。岁值壬戌。即其母丧重回之年也。其除夕之夜。忽做一梦。慈颜依稀。急进攀裾。自发号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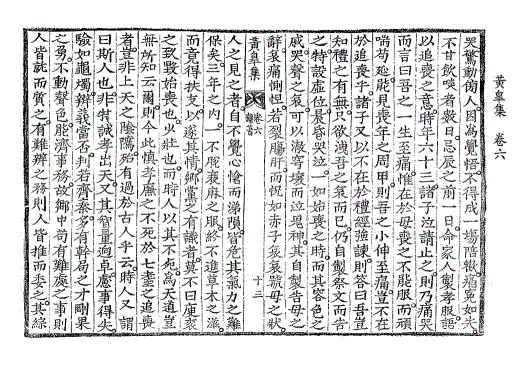 哭。惊动傍人。因为觉悟。不得成一场陪欢。痛冤如失。不甘饮啖者数日。忌辰之前一日。命家人制孝服。语以追丧之意。时年六十三。诸子泣请止之。则乃痛哭而言曰吾之一生至痛。惟在于母丧之不能服。而顽喘苟延。能见丧年之周甲。则吾之小伸至痛。岂不在于追丧乎。诸子又以不在于礼经强谏。则答曰吾岂知礼之有无。只欲泄吾之哀而已。仍自制祭文而告之。特设虚位。晨昏哭泣。一如始丧之时。而其容色之戚。哭声之哀。可以澈穹壤而泣鬼神。其自制告母之辞。哀痛恻怛。若裂肠肝。而恍如赤子哀哀号母之状。人之见之者。自不觉心怆而涕陨。皆危其气力之难保矣。三年之内。一不脱衰麻之服。终不进草木之滋。而竟得扶支。以遂其情。乡党之有识者。莫不曰庾衮之致毁始丧也。少壮也。而时人以其不死。为天道岂无所知云尔。则今此慎孝廉之不死于七耋之追丧者。岂非上天之阴骘。殆有过于古人乎云。时人又谓曰斯人也。非特诚孝出天。又其智量迥卓。虑事得失。验如龟烛。辨义当否。判若齐秦。多有干局之才刚果之勇。不动声色。能济事务。故乡中苟有难处之事则人皆就而质之。有难辨之务则人皆推而委之。其综
哭。惊动傍人。因为觉悟。不得成一场陪欢。痛冤如失。不甘饮啖者数日。忌辰之前一日。命家人制孝服。语以追丧之意。时年六十三。诸子泣请止之。则乃痛哭而言曰吾之一生至痛。惟在于母丧之不能服。而顽喘苟延。能见丧年之周甲。则吾之小伸至痛。岂不在于追丧乎。诸子又以不在于礼经强谏。则答曰吾岂知礼之有无。只欲泄吾之哀而已。仍自制祭文而告之。特设虚位。晨昏哭泣。一如始丧之时。而其容色之戚。哭声之哀。可以澈穹壤而泣鬼神。其自制告母之辞。哀痛恻怛。若裂肠肝。而恍如赤子哀哀号母之状。人之见之者。自不觉心怆而涕陨。皆危其气力之难保矣。三年之内。一不脱衰麻之服。终不进草木之滋。而竟得扶支。以遂其情。乡党之有识者。莫不曰庾衮之致毁始丧也。少壮也。而时人以其不死。为天道岂无所知云尔。则今此慎孝廉之不死于七耋之追丧者。岂非上天之阴骘。殆有过于古人乎云。时人又谓曰斯人也。非特诚孝出天。又其智量迥卓。虑事得失。验如龟烛。辨义当否。判若齐秦。多有干局之才刚果之勇。不动声色。能济事务。故乡中苟有难处之事则人皆就而质之。有难辨之务则人皆推而委之。其综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2L 页
 理贞干。人所难及。而观其一二之细事。亦可知恬于财必于义也。尝见其换马于人。过了数年。所换之马倍直于旧马。则即以所倍之直。尽给其人。其人固辞。而强令必受。尝卖家垈。得钱百缗。贸置木花于永峡人家。一日其人乃以贼失为言。而了无一辞。脱然弃之。或劝其呈官推治。自当推寻。则谢曰此非仁人之所为。而财之于人。都是身外之物。况吾平生拙性。非关系祖先之事。则虽以奴名。未尝呈状于法司。则岂可为些少财货而破我宿诫。以困夫无罪之人乎。遂弃而不推。其弘量厚德。亦非人所可及者云。风声所暨。凡有秉彝者。莫不诚服。而至于道内儒生四五百人。累发呈状。而竟未蒙宾兴之典。惜哉。丙子之岁。以天年终于三省堂。得年七十七。
理贞干。人所难及。而观其一二之细事。亦可知恬于财必于义也。尝见其换马于人。过了数年。所换之马倍直于旧马。则即以所倍之直。尽给其人。其人固辞。而强令必受。尝卖家垈。得钱百缗。贸置木花于永峡人家。一日其人乃以贼失为言。而了无一辞。脱然弃之。或劝其呈官推治。自当推寻。则谢曰此非仁人之所为。而财之于人。都是身外之物。况吾平生拙性。非关系祖先之事。则虽以奴名。未尝呈状于法司。则岂可为些少财货而破我宿诫。以困夫无罪之人乎。遂弃而不推。其弘量厚德。亦非人所可及者云。风声所暨。凡有秉彝者。莫不诚服。而至于道内儒生四五百人。累发呈状。而竟未蒙宾兴之典。惜哉。丙子之岁。以天年终于三省堂。得年七十七。噫耳目之所睹记。斯人之至行懿德。岂止为一时之矜式。抑可为百世之表范。而身没草野。微而不显。恐其年代寝远。湮没无传。略记其梗槩如右。而窃寓效为金忠烈作传之意。
烈妇孺人瑞山郑氏传
噫。天地间纯刚至正之气。亘彻宇宙而不灭者。今又见于长水县士人西门培妻瑞山郑氏之贞烈也。郑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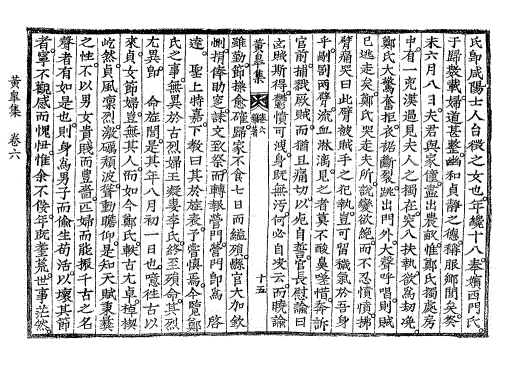 氏即咸阳士人台徵之女也。年才十八。奉嫔西门氏。于归数载。妇道甚整。幽和贞静之德。称服乡闾矣。癸未六月八日。夫君与家僮。尽出农亩。惟郑氏独处房中。有一凶汉过见夫人之独在。突入扶执。欲为劫浼。郑氏大惊奋拒。衣裾断裂。跳出门外。大声呼唱。则贼已逃走矣。郑氏哭走夫所。说变欲绝。而不忍愤愤。拂臂痛哭曰此臂被贼手之犯执。岂可留秽气于吾身乎。剐割两臂。流血淋漓。见之者莫不酸鼻嗟惜。奔诉官前。捕戮厥贼。而犹且痛切。以死自誓。官长慰谕曰凶贼斯得。郁愤可泄。身既无污。何必自决云。而晓谕虽勤。节操愈确。归家不食七日而缢殒。县官大加钦恻。捐俸助窆。诔文致祭。而转报营门。营门即为 启达。 圣上特嘉。下教曰其于旌表。予尝慎焉。今览郑氏之事。无异于古烈妇王凝妻李氏。终至殒命。其烈尤异。即 命旌闾。是其年八月初一日也。噫往古以来。贞女节妇。岂无其人。而如今郑氏。轶古尤卓。棹楔屹然。贞风凛烈。激砺颓波。耸动瞻仰。是知天赋秉彝之性。不以男女贵贱而礼啬。匹妇而能振千古之名声者有如是也。则身为男子而偷生苟活。以坏其节者。宁不观感而愧忸。惟余不佞。年既耋荒。世事茫然。
氏即咸阳士人台徵之女也。年才十八。奉嫔西门氏。于归数载。妇道甚整。幽和贞静之德。称服乡闾矣。癸未六月八日。夫君与家僮。尽出农亩。惟郑氏独处房中。有一凶汉过见夫人之独在。突入扶执。欲为劫浼。郑氏大惊奋拒。衣裾断裂。跳出门外。大声呼唱。则贼已逃走矣。郑氏哭走夫所。说变欲绝。而不忍愤愤。拂臂痛哭曰此臂被贼手之犯执。岂可留秽气于吾身乎。剐割两臂。流血淋漓。见之者莫不酸鼻嗟惜。奔诉官前。捕戮厥贼。而犹且痛切。以死自誓。官长慰谕曰凶贼斯得。郁愤可泄。身既无污。何必自决云。而晓谕虽勤。节操愈确。归家不食七日而缢殒。县官大加钦恻。捐俸助窆。诔文致祭。而转报营门。营门即为 启达。 圣上特嘉。下教曰其于旌表。予尝慎焉。今览郑氏之事。无异于古烈妇王凝妻李氏。终至殒命。其烈尤异。即 命旌闾。是其年八月初一日也。噫往古以来。贞女节妇。岂无其人。而如今郑氏。轶古尤卓。棹楔屹然。贞风凛烈。激砺颓波。耸动瞻仰。是知天赋秉彝之性。不以男女贵贱而礼啬。匹妇而能振千古之名声者有如是也。则身为男子而偷生苟活。以坏其节者。宁不观感而愧忸。惟余不佞。年既耋荒。世事茫然。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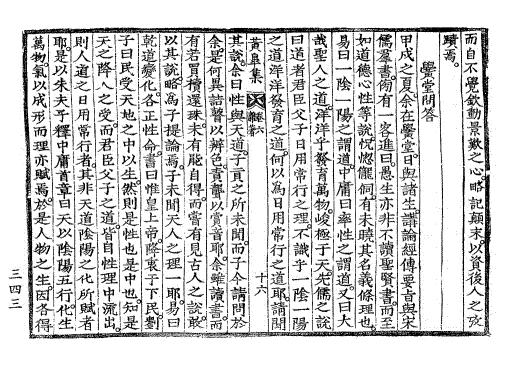 而自不觉钦动景叹之心。略记颠末。以资后人之考迹焉。
而自不觉钦动景叹之心。略记颠末。以资后人之考迹焉。黉堂问答
甲戌之夏。余在黉堂。日与诸生。讲论经传要旨与宋儒群书。傍有一客进曰。愚生亦非不读圣贤书。而至如道德心性等说。恍惚儱侗。有未晓其名义条理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曰率性之谓道。又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先儒之说曰道者君臣父子日用常行之理。不识乎一阴一阳之道洋洋发育之道。何以为日用常行之道耶。请闻其说。余曰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闻。而子今请问于余。是何异诘𥌒以辨色。责聋以赏音耶。余虽读书。而有若买椟还珠。未有能自得。而尝有见古人之说。敢以其说。略为子提论焉。子未闻天人之理一耶。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然则是性也是中也。知是天之降人之受。而君臣父子之道。皆自性理中流出。则人道之日用常行者。其非天道阴阳之化所赋者耶。是以朱夫子释中庸首章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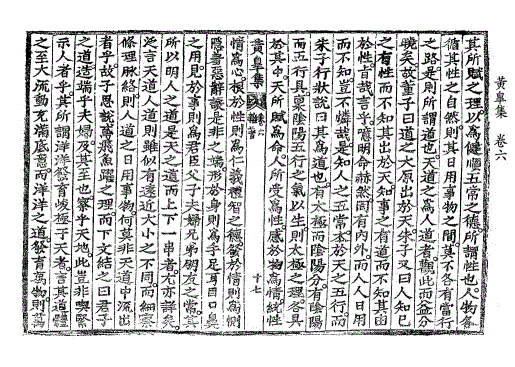 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天道之为人道者。观此而益分晓矣。故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朱子又曰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旨哉言乎。噫明命赫然。罔有内外。而人人日用而不知。岂不怜哉。是知人之五常。本于天之五行。而朱子行状说曰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其所以明人之道是天之道而上下一串者。尤亦详矣。泛言天道人道则虽似有远近大小之不同。而细察条理脉络。则人道之日用事物。何莫非天道中流出者乎。故子思说鸢飞鱼跃之理。而下文结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岂非吃紧示人者乎。其所谓洋洋发育峻极于天者。言其道体之至大流动充满底意。而洋洋之道。发育万物。则万
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天道之为人道者。观此而益分晓矣。故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朱子又曰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旨哉言乎。噫明命赫然。罔有内外。而人人日用而不知。岂不怜哉。是知人之五常。本于天之五行。而朱子行状说曰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其所以明人之道是天之道而上下一串者。尤亦详矣。泛言天道人道则虽似有远近大小之不同。而细察条理脉络。则人道之日用事物。何莫非天道中流出者乎。故子思说鸢飞鱼跃之理。而下文结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岂非吃紧示人者乎。其所谓洋洋发育峻极于天者。言其道体之至大流动充满底意。而洋洋之道。发育万物。则万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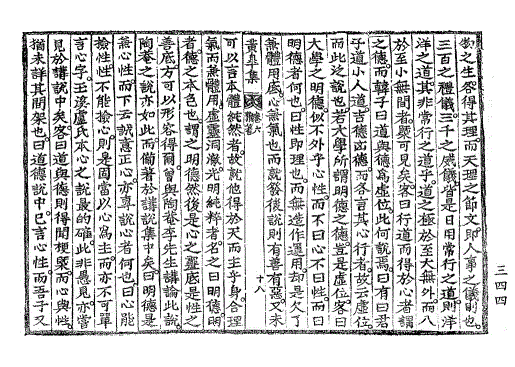 物之生。各得其理。而天理之节文。即人事之仪则也。三百之礼仪。三千之威仪。皆是日用常行之道。则洋洋之道。其非常行之道乎。道之极于至大无外。而入于至小无间者。槩可见矣。客曰行道而得于心者谓之德。而韩子曰道与德为虚位。此何说焉。曰有曰君子道小人道。吉德凶德。而各言其心行者。故云虚位。而此泛说也。若大学所谓明德之德。岂是虚位。客曰大学之明德。似不外乎心性。而不曰心不曰性。而曰明德者何也。曰性即理也。而无造作运用。却是欠了兼体用底。心兼气也而就发后说则有善有恶。又未可以言本体纯然者。故就他得于天而主乎身。合理气而兼体用。虚灵洞澈。光明纯粹者。名之曰明德。明者。德之本色也。谓之明德然后是心之灵底是性之善底。方可以形容得尔。曾与陶庵李先生讲论此说。陶庵之说亦如此。而备著于讲说集中矣。曰明德是兼心性。而下云诚意正心。亦专说心者何也。曰心能捡性。性不能捡心。则是固当以心为主。而亦不可单言心字。玉溪卢氏本心之说最的确。此非愚见。亦尝见于讲说中矣。客曰道与德则得闻梗槩。而心与性。犹未详其间架也。曰道德说中。已言心性。而吾子又
物之生。各得其理。而天理之节文。即人事之仪则也。三百之礼仪。三千之威仪。皆是日用常行之道。则洋洋之道。其非常行之道乎。道之极于至大无外。而入于至小无间者。槩可见矣。客曰行道而得于心者谓之德。而韩子曰道与德为虚位。此何说焉。曰有曰君子道小人道。吉德凶德。而各言其心行者。故云虚位。而此泛说也。若大学所谓明德之德。岂是虚位。客曰大学之明德。似不外乎心性。而不曰心不曰性。而曰明德者何也。曰性即理也。而无造作运用。却是欠了兼体用底。心兼气也而就发后说则有善有恶。又未可以言本体纯然者。故就他得于天而主乎身。合理气而兼体用。虚灵洞澈。光明纯粹者。名之曰明德。明者。德之本色也。谓之明德然后是心之灵底是性之善底。方可以形容得尔。曾与陶庵李先生讲论此说。陶庵之说亦如此。而备著于讲说集中矣。曰明德是兼心性。而下云诚意正心。亦专说心者何也。曰心能捡性。性不能捡心。则是固当以心为主。而亦不可单言心字。玉溪卢氏本心之说最的确。此非愚见。亦尝见于讲说中矣。客曰道与德则得闻梗槩。而心与性。犹未详其间架也。曰道德说中。已言心性。而吾子又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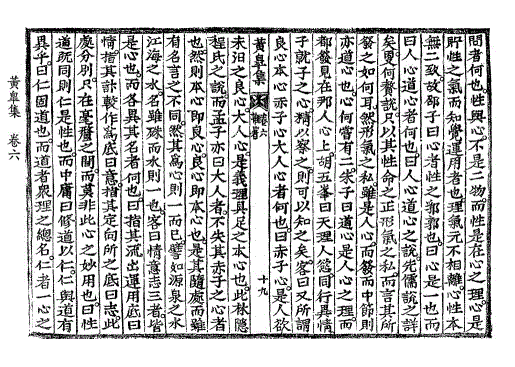 问者何也。性与心。不是二物。而性是在心之理。心是贮性之气而知觉运用者也。理气元不相离。心性本无二致。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曰心是一也而曰人心道心者何也。曰人心道心之说。先儒说之详矣。更何赘说。只以其性命之正形气之私。而言其所发之如何耳。然形气之私。虽是人心。而发而中节则亦道心也。心何尝有二。朱子曰道心是人心之理。而都发见在那人心上。胡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子就子之心。精以察之。则可以知之矣。客曰又所谓良心本心赤子心大人心者何也。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汩之良心。大人心。是义理具足之本心也。此林隐程氏之说。而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则本心即良心。良心即本心也。是其随处而虽有名言之不同。然其为心则一而已。譬如源泉之水江海之水。名虽殊而水则一也。客曰情意志三者。皆是心也。而各异其名者何也。曰指其流出运用底曰情。指其计较作为底曰意。指其定向所之底曰志。此处分别。只在毫釐之间。而莫非此心之妙用也。曰性道既同则仁是性也。而中庸曰修道以仁。仁与道有异乎。曰仁固道也。而道者众理之总名。仁者一心之
问者何也。性与心。不是二物。而性是在心之理。心是贮性之气而知觉运用者也。理气元不相离。心性本无二致。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曰心是一也而曰人心道心者何也。曰人心道心之说。先儒说之详矣。更何赘说。只以其性命之正形气之私。而言其所发之如何耳。然形气之私。虽是人心。而发而中节则亦道心也。心何尝有二。朱子曰道心是人心之理。而都发见在那人心上。胡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子就子之心。精以察之。则可以知之矣。客曰又所谓良心本心赤子心大人心者何也。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汩之良心。大人心。是义理具足之本心也。此林隐程氏之说。而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则本心即良心。良心即本心也。是其随处而虽有名言之不同。然其为心则一而已。譬如源泉之水江海之水。名虽殊而水则一也。客曰情意志三者。皆是心也。而各异其名者何也。曰指其流出运用底曰情。指其计较作为底曰意。指其定向所之底曰志。此处分别。只在毫釐之间。而莫非此心之妙用也。曰性道既同则仁是性也。而中庸曰修道以仁。仁与道有异乎。曰仁固道也。而道者众理之总名。仁者一心之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5L 页
 全德也。以道言则冲漠散殊而莫见其实。惟求之于吾心亲切处用工。然后可见其为道之实而修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是有二致也。客曰诚敬名义似不同。而蔡九峰书序曰曰德曰仁曰敬曰诚。名虽殊而理则一。德与仁之理一。固是然矣。而敬与诚之理一。愚未晓也。曰敬是竦然如畏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之名。意思不同。然是诚也在道则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若无此心之戒惧凝聚维持主宰。则何以致实理之直上直下贯澈无间而德之聚仁之熟也。敬则诚存。诚由敬立。而大本达道。皆是此心诚敬之妙。则蔡氏之说盖谓此也。程伯子有言曰天地设位。易行于其中。只是敬也。亦言其实理之未尝间断也。曰然则诚为仁智道德之本乎。曰尝见谭氏说其名义曰诚之体为仁。诚之用为智。诚之实理可据曰德。诚之实理可由曰道。此言可谓端的也。客曰理气元不相离。所谓理者何也。所谓气者何也。曰理气之论。濂洛群哲与我东诸贤之辨说详矣。愚何敢更赘。大槩言之。则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气也。理者气之主宰。而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着。既非一物。亦非二物。大
全德也。以道言则冲漠散殊而莫见其实。惟求之于吾心亲切处用工。然后可见其为道之实而修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是有二致也。客曰诚敬名义似不同。而蔡九峰书序曰曰德曰仁曰敬曰诚。名虽殊而理则一。德与仁之理一。固是然矣。而敬与诚之理一。愚未晓也。曰敬是竦然如畏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之名。意思不同。然是诚也在道则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若无此心之戒惧凝聚维持主宰。则何以致实理之直上直下贯澈无间而德之聚仁之熟也。敬则诚存。诚由敬立。而大本达道。皆是此心诚敬之妙。则蔡氏之说盖谓此也。程伯子有言曰天地设位。易行于其中。只是敬也。亦言其实理之未尝间断也。曰然则诚为仁智道德之本乎。曰尝见谭氏说其名义曰诚之体为仁。诚之用为智。诚之实理可据曰德。诚之实理可由曰道。此言可谓端的也。客曰理气元不相离。所谓理者何也。所谓气者何也。曰理气之论。濂洛群哲与我东诸贤之辨说详矣。愚何敢更赘。大槩言之。则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气也。理者气之主宰。而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着。既非一物。亦非二物。大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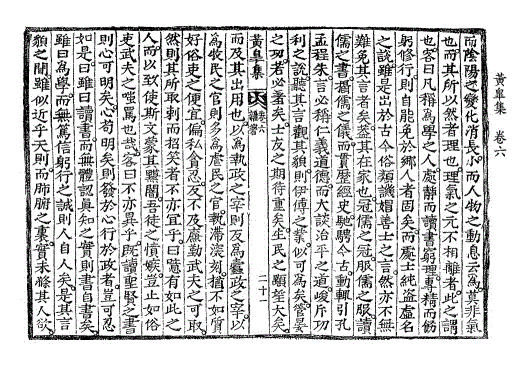 而阴阳之变化消长。小而人物之动息云为。莫非气也。而其所以然者理也。理气之元不相离者。此之谓也。客曰凡称为学之人。处静而读书穷理。专精而饬躬修行。则自能免于乡人者固矣。而处士纯盗虚名之说。虽是出于古今俗类讥媢善士之言。然亦不无难免其言者矣。盖其在家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读儒之书。摄儒之仪。而贯历经史。驰骋今古。动辄引孔孟程朱。言必称仁义道德。而大谈治平之道。峻斥功利之说。听其言观其貌。则伊傅之业。似可为矣。管晏之功。若必羞矣。士友之期待重矣。生民之颙望大矣。而及其出用也。以为执政之宰则反为蠹政之宰。以为牧民之官则多为虐民之官。执滞深刻。犹不如质好俗吏之便宜。偏私贪忍。反不及廉勤武夫之可取。然则其所取刺而招笑者不亦宜乎。曰噫有如此之人。而以致使斯文蒙其黮闇。吾徒之愤嫉。岂止如俗吏武夫之嗤骂也哉。客曰不亦异乎。既读圣贤之书则心可明矣。心苟明矣则发于心行于政者。岂可忍如是。曰虽曰读书。而无体认真知之实则书自书矣。虽曰为学。而无笃信躬行之诚则人自人矣。是其言貌之间。虽似近乎天则。而肺腑之里。实未涤其人欲。
而阴阳之变化消长。小而人物之动息云为。莫非气也。而其所以然者理也。理气之元不相离者。此之谓也。客曰凡称为学之人。处静而读书穷理。专精而饬躬修行。则自能免于乡人者固矣。而处士纯盗虚名之说。虽是出于古今俗类讥媢善士之言。然亦不无难免其言者矣。盖其在家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读儒之书。摄儒之仪。而贯历经史。驰骋今古。动辄引孔孟程朱。言必称仁义道德。而大谈治平之道。峻斥功利之说。听其言观其貌。则伊傅之业。似可为矣。管晏之功。若必羞矣。士友之期待重矣。生民之颙望大矣。而及其出用也。以为执政之宰则反为蠹政之宰。以为牧民之官则多为虐民之官。执滞深刻。犹不如质好俗吏之便宜。偏私贪忍。反不及廉勤武夫之可取。然则其所取刺而招笑者不亦宜乎。曰噫有如此之人。而以致使斯文蒙其黮闇。吾徒之愤嫉。岂止如俗吏武夫之嗤骂也哉。客曰不亦异乎。既读圣贤之书则心可明矣。心苟明矣则发于心行于政者。岂可忍如是。曰虽曰读书。而无体认真知之实则书自书矣。虽曰为学。而无笃信躬行之诚则人自人矣。是其言貌之间。虽似近乎天则。而肺腑之里。实未涤其人欲。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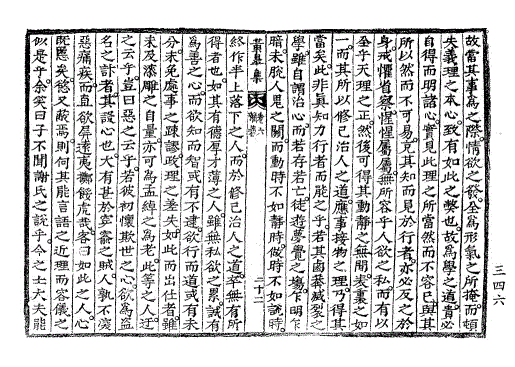 故当其事为之际。情欲之发。全为形气之所掩。而顿失义理之本心。致有如此之弊也。故为学之道。贵必自得而明诸心。实见此理之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充其知而见于行者。亦必反之于身。戒惧省察。惺惺属属。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然后可得其动静之无间。表里之如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道。应事接物之理。乃得其当矣。此非真知力行者而能之乎。若其卤莽灭裂之学。虽自谓治心。而若存若亡。徒游梦觉之场。乍明乍暗。未脱人鬼之关。而动时不如静时。做时不如说时。终作半上落下之人。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卒无有所得者也。如其有德厚才薄之人。虽无私欲之累。诚有为善之心。而欲知而智或有不逮。欲行而道或有未分。未免处事之疏谬。政理之差失。如此而出仕者。虽未及漆雕之自量。亦可为孟绰之为老。此等之人。迂之云乎。岂曰恶之云乎。若彼初怀欺世之心。欲为盗名之计者。其设心也。大有甚于穿窬之贼。人孰不深恶痛疾。而直欲屏远夷掷馁虎哉。客曰如此之人。心既慝矣。欲又蔽焉。则何其能言语之近理而容仪之似是乎。余笑曰子不闻谢氏之说乎。今之士大夫能
故当其事为之际。情欲之发。全为形气之所掩。而顿失义理之本心。致有如此之弊也。故为学之道。贵必自得而明诸心。实见此理之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充其知而见于行者。亦必反之于身。戒惧省察。惺惺属属。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然后可得其动静之无间。表里之如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道。应事接物之理。乃得其当矣。此非真知力行者而能之乎。若其卤莽灭裂之学。虽自谓治心。而若存若亡。徒游梦觉之场。乍明乍暗。未脱人鬼之关。而动时不如静时。做时不如说时。终作半上落下之人。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卒无有所得者也。如其有德厚才薄之人。虽无私欲之累。诚有为善之心。而欲知而智或有不逮。欲行而道或有未分。未免处事之疏谬。政理之差失。如此而出仕者。虽未及漆雕之自量。亦可为孟绰之为老。此等之人。迂之云乎。岂曰恶之云乎。若彼初怀欺世之心。欲为盗名之计者。其设心也。大有甚于穿窬之贼。人孰不深恶痛疾。而直欲屏远夷掷馁虎哉。客曰如此之人。心既慝矣。欲又蔽焉。则何其能言语之近理而容仪之似是乎。余笑曰子不闻谢氏之说乎。今之士大夫能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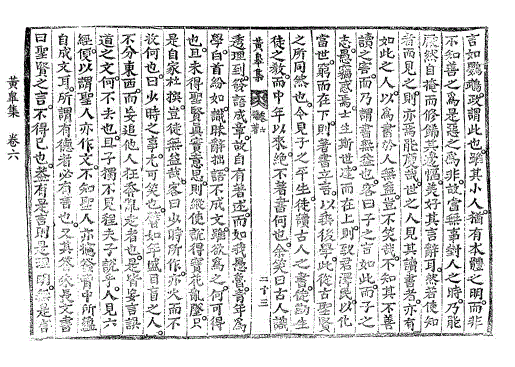 言如鹦鹉。政谓此也。虽其小人。犹有本体之明。而非不知善之为是恶之为非。故当无事对人之时。乃能厌然自掩而修饰其边幅。美好其言辞耳。然若使知者而见之。则亦焉能廋哉。世之人见其读书者。亦有如此之人。以为书于人无益。岂不笑哉。不知其不善读之害。而乃谓书无益也。客曰子之言如此。而子之志。愚窃惑焉。士生斯世。达而在上。则致君泽民。以化当世。穷而在下。则著书立言。以垂后学。此从古圣贤之所同然也。今见子之平生。徒读古人之书。徒勤生徒之教。而中年以来。绝不著书何也。余笑曰古人识透理到。发语成章。故自有著述。而如我愚鲁。青年为学。白首纷如。识昧辞拙。语不成文。虽欲为之。何可得也。且未得圣贤真实意思。则纵使说得宝花乱坠。只是自家杜撰。岂徒无益哉。客曰少时所作。亦火而不收何也。曰少时之事。尤可笑也。譬如年盛目盲之人。不分东西。而妄追他人狂奔乱走者也。是皆妄言误道之文。何不去也。且子独不见程夫子说乎。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又其答朱长文书曰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
言如鹦鹉。政谓此也。虽其小人。犹有本体之明。而非不知善之为是恶之为非。故当无事对人之时。乃能厌然自掩而修饰其边幅。美好其言辞耳。然若使知者而见之。则亦焉能廋哉。世之人见其读书者。亦有如此之人。以为书于人无益。岂不笑哉。不知其不善读之害。而乃谓书无益也。客曰子之言如此。而子之志。愚窃惑焉。士生斯世。达而在上。则致君泽民。以化当世。穷而在下。则著书立言。以垂后学。此从古圣贤之所同然也。今见子之平生。徒读古人之书。徒勤生徒之教。而中年以来。绝不著书何也。余笑曰古人识透理到。发语成章。故自有著述。而如我愚鲁。青年为学。白首纷如。识昧辞拙。语不成文。虽欲为之。何可得也。且未得圣贤真实意思。则纵使说得宝花乱坠。只是自家杜撰。岂徒无益哉。客曰少时所作。亦火而不收何也。曰少时之事。尤可笑也。譬如年盛目盲之人。不分东西。而妄追他人狂奔乱走者也。是皆妄言误道之文。何不去也。且子独不见程夫子说乎。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又其答朱长文书曰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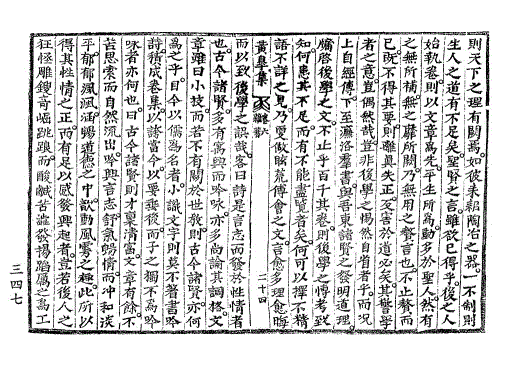 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其警学者之意。岂偶然哉。岂非后学之惕然自省者乎。而况上自经传。下至濂洛群书。与吾东诸贤之发明道理。牖启后学之文。不止乎百千其卷。则后学之博考致知。何患其不足。而有不能尽览者矣。何可以择不精语不详之见。乃更做眩荒傅会之文。言愈多理愈晦而以致后学之误哉。客曰诗是言志而发于性情者也。古今诸贤。多有寓兴而吟咏。亦多尚论其调格。文章虽曰小技。而若不有关于世教。则古今诸贤。亦何为之乎。目今以儒为名者。小识文字则莫不著书吟诗。积成卷集。以誇当今。以要垂后。而子之独不为吟咏者亦何也。曰古今诸贤则才禀清富。文章有馀。不苦思索而自然流出。吟兴言志。舒气畅情。而冲和淡平。郁郁沨沨。涵畅道德之中。歆动风雩之趣。此所以得其性情之正。而有足以感发兴起者。岂若后人之狂怪雕锼奇崛跳踉。而酸咸苦涩发扬蹈厉之为工
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其警学者之意。岂偶然哉。岂非后学之惕然自省者乎。而况上自经传。下至濂洛群书。与吾东诸贤之发明道理。牖启后学之文。不止乎百千其卷。则后学之博考致知。何患其不足。而有不能尽览者矣。何可以择不精语不详之见。乃更做眩荒傅会之文。言愈多理愈晦而以致后学之误哉。客曰诗是言志而发于性情者也。古今诸贤。多有寓兴而吟咏。亦多尚论其调格。文章虽曰小技。而若不有关于世教。则古今诸贤。亦何为之乎。目今以儒为名者。小识文字则莫不著书吟诗。积成卷集。以誇当今。以要垂后。而子之独不为吟咏者亦何也。曰古今诸贤则才禀清富。文章有馀。不苦思索而自然流出。吟兴言志。舒气畅情。而冲和淡平。郁郁沨沨。涵畅道德之中。歆动风雩之趣。此所以得其性情之正。而有足以感发兴起者。岂若后人之狂怪雕锼奇崛跳踉。而酸咸苦涩发扬蹈厉之为工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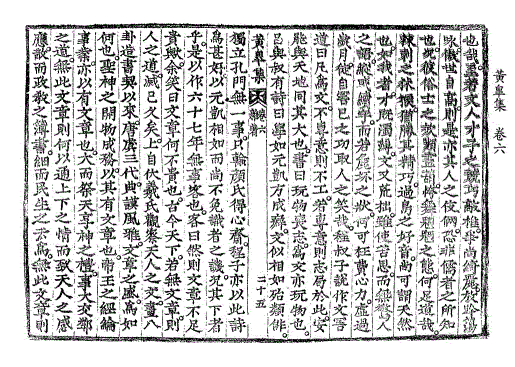 也哉。至若文人才子之竞巧敲椎(一作推)。争尚绮丽。放吟荡咏。傲世自高。则是亦其人之伎俩。恐非儒者之所知也。况彼俗士之效嚬画葫。恗舞魍魉之态。何足道哉。棘刺之𤝞(一作沐)猴。犹胜其精巧。过鸟之好音。尚可谓天然也。如我者。才既浊薄。文又荒拙。虽使苦思。而无惊人之语。纵或续手。而若粗坏之状。何可枉费心力。虚过岁月。徒自害己之功取人之笑哉。程叔子说作文害道曰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曰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程子亦以此诗为甚好。以元凯相如而尚不免识者之讥。况其下者乎。是以作六十七年无事客也。客曰然则文章不足贵欤。余笑曰文章何不贵也。古今天下。若无文章。则人之道。灭已久矣。上自伏羲氏观察天人之文。画八卦造书契以来。唐虞三代。典谟风雅。文章之盛。为如何也。圣神之开物成务。以其有文章也。帝王之经纶事业。亦以有文章也。大而祭天享神之礼。事大交邻之道。无此文章则何以通上下之情而致天人之感应。散而政教之簿书。细而民生之云为。无此文章则
也哉。至若文人才子之竞巧敲椎(一作推)。争尚绮丽。放吟荡咏。傲世自高。则是亦其人之伎俩。恐非儒者之所知也。况彼俗士之效嚬画葫。恗舞魍魉之态。何足道哉。棘刺之𤝞(一作沐)猴。犹胜其精巧。过鸟之好音。尚可谓天然也。如我者。才既浊薄。文又荒拙。虽使苦思。而无惊人之语。纵或续手。而若粗坏之状。何可枉费心力。虚过岁月。徒自害己之功取人之笑哉。程叔子说作文害道曰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曰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程子亦以此诗为甚好。以元凯相如而尚不免识者之讥。况其下者乎。是以作六十七年无事客也。客曰然则文章不足贵欤。余笑曰文章何不贵也。古今天下。若无文章。则人之道。灭已久矣。上自伏羲氏观察天人之文。画八卦造书契以来。唐虞三代。典谟风雅。文章之盛。为如何也。圣神之开物成务。以其有文章也。帝王之经纶事业。亦以有文章也。大而祭天享神之礼。事大交邻之道。无此文章则何以通上下之情而致天人之感应。散而政教之簿书。细而民生之云为。无此文章则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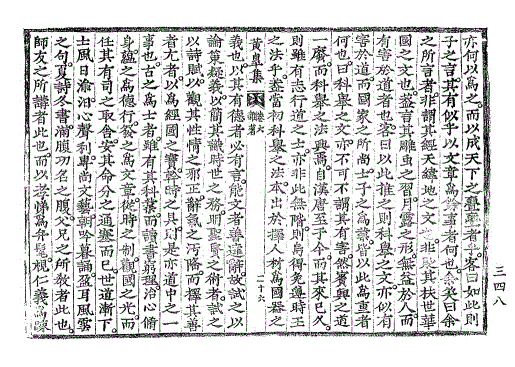 亦何以为之。而以成天下之亹亹者乎。客曰如此则子之言。其有似乎以文章为馀事者何也。余笑曰余之所言者。非谓其经天纬地之文也。非贬其扶世华国之文也。盖言其雕虫之习。月露之形。无益于人。而有害于道者也。客曰以此推之则科举之文。亦似有害于道。而国家之所尚。士子之为业。皆以此为重者何也。曰科举之文。亦不可不谓其有害。然宾兴之道一废。而科举之法兴焉。自汉唐至于今。而其来已久。则虽有志行道之士。亦非此无阶。则乌得免遵时王之法乎。盖当初科举之法。本出于择人材为国器之义也。以其有德者必有言。能文者善达辞。故试之以论策疑义。以简其识时世之务。明圣贤之术者。试之以诗赋。以观其性情之邪正。辞气之污隆。而择其善者尤者。以为经国之宝。干时之具。则是亦道中之一事也。古之为士者。虽有其科业。而读书穷理。治心脩身。蕴之为德行。发之为文章。从时之制。观国之光。而任其有司之取舍。安其命分之通塞而已。世道渐下。士风日渝。汩心声利。专尚文艺。朝吟暮诵。盈耳风云之句。夏诗冬书。满腹功名之腹。父兄之所教者此也。师友之所讲者此也。而以孝悌为弁髦。视仁义为疏
亦何以为之。而以成天下之亹亹者乎。客曰如此则子之言。其有似乎以文章为馀事者何也。余笑曰余之所言者。非谓其经天纬地之文也。非贬其扶世华国之文也。盖言其雕虫之习。月露之形。无益于人。而有害于道者也。客曰以此推之则科举之文。亦似有害于道。而国家之所尚。士子之为业。皆以此为重者何也。曰科举之文。亦不可不谓其有害。然宾兴之道一废。而科举之法兴焉。自汉唐至于今。而其来已久。则虽有志行道之士。亦非此无阶。则乌得免遵时王之法乎。盖当初科举之法。本出于择人材为国器之义也。以其有德者必有言。能文者善达辞。故试之以论策疑义。以简其识时世之务。明圣贤之术者。试之以诗赋。以观其性情之邪正。辞气之污隆。而择其善者尤者。以为经国之宝。干时之具。则是亦道中之一事也。古之为士者。虽有其科业。而读书穷理。治心脩身。蕴之为德行。发之为文章。从时之制。观国之光。而任其有司之取舍。安其命分之通塞而已。世道渐下。士风日渝。汩心声利。专尚文艺。朝吟暮诵。盈耳风云之句。夏诗冬书。满腹功名之腹。父兄之所教者此也。师友之所讲者此也。而以孝悌为弁髦。视仁义为疏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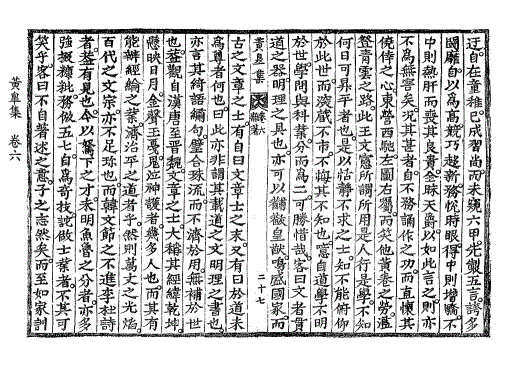 迂。自在童稚。已成习尚。而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誇多斗靡。自以为高。竞巧趍新。务悦时眼。得中则增骄。不中则热肝而丧其良贵。全昧天爵。以如此言之。则亦不为无害矣。况其甚者。自不务诵作之功。而直怀其侥倖之心。东营西驰。左图右嘱。而笑他黄卷之劳。滥登青云之路。此王文宪所谓所用是人行是学。不知何日可升平者也。是以恬静不求之士。知不能俯仰于此世。而深藏不市。不悔其不知也。噫自道学不明于世。学问与科业。分而为二。可胜惜哉。客曰文者贯道之器。明理之具也。亦可以黼黻皇猷。鸣盛国家。而古之文章之士。有自曰文章士之末。又有曰于道未为尊者何也。曰此亦非谓其载道之文明理之书也。亦言其绮语绣句。璧合珠流。而不济于用。无补于世也。盖观自汉唐至晋魏。文章之士。大称其经纬乾坤。悬映日月。金声玉戛。鬼泣神护者。几多人也。而其有能办经纶之业。济治平之道者乎。然则万丈之光焰。百代之文宗。亦不足珍也。而韩文节之不进李杜诗者。盖有见也。今以驽下之才。未明鱼鲁之分者。亦多强掇糠秕。务仿五七。自为奇技。詑做士业者。不其可笑乎。客曰不自著述之意。子之志然矣。而至如家训
迂。自在童稚。已成习尚。而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誇多斗靡。自以为高。竞巧趍新。务悦时眼。得中则增骄。不中则热肝而丧其良贵。全昧天爵。以如此言之。则亦不为无害矣。况其甚者。自不务诵作之功。而直怀其侥倖之心。东营西驰。左图右嘱。而笑他黄卷之劳。滥登青云之路。此王文宪所谓所用是人行是学。不知何日可升平者也。是以恬静不求之士。知不能俯仰于此世。而深藏不市。不悔其不知也。噫自道学不明于世。学问与科业。分而为二。可胜惜哉。客曰文者贯道之器。明理之具也。亦可以黼黻皇猷。鸣盛国家。而古之文章之士。有自曰文章士之末。又有曰于道未为尊者何也。曰此亦非谓其载道之文明理之书也。亦言其绮语绣句。璧合珠流。而不济于用。无补于世也。盖观自汉唐至晋魏。文章之士。大称其经纬乾坤。悬映日月。金声玉戛。鬼泣神护者。几多人也。而其有能办经纶之业。济治平之道者乎。然则万丈之光焰。百代之文宗。亦不足珍也。而韩文节之不进李杜诗者。盖有见也。今以驽下之才。未明鱼鲁之分者。亦多强掇糠秕。务仿五七。自为奇技。詑做士业者。不其可笑乎。客曰不自著述之意。子之志然矣。而至如家训黄皋集卷之六 第 3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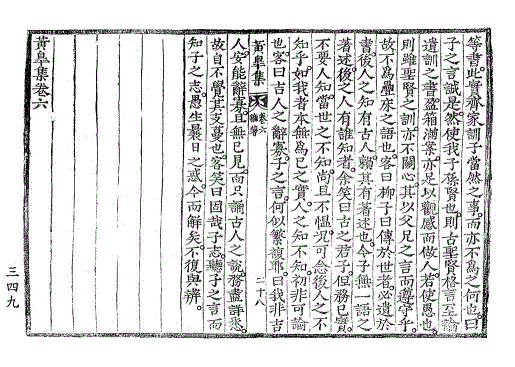 等书。此实齐家训子当然之事。而亦不为之何也。曰子之言诚是。然使我子孙贤也。则古圣贤格言至论遗训之书。盈箱满案。亦足以观感而做人。若使愚也。则虽圣贤之训。亦不关心。其以父兄之言而遵守乎。故不为叠床之语也。客曰柳子曰传于世者。必遗于书。后人之知有古人。赖其有著述也。今子无一语之著述。后之人有谁知者。余笑曰古之君子。但务己实。不要人知。当世之不知。尚且不愠。况可念后人之不知乎。如我者本无为己之实。人之知不知。初非可论也。客曰吉人之辞寡。子之言。何似繁复耶。曰我非吉人。安能辞寡。且无己见。而只诵古人之说。务尽详悉。故自不觉其支蔓也。客笑曰固哉子志。听子之言而知子之志。愚生曩日之惑。今而解矣。不复与辨。
等书。此实齐家训子当然之事。而亦不为之何也。曰子之言诚是。然使我子孙贤也。则古圣贤格言至论遗训之书。盈箱满案。亦足以观感而做人。若使愚也。则虽圣贤之训。亦不关心。其以父兄之言而遵守乎。故不为叠床之语也。客曰柳子曰传于世者。必遗于书。后人之知有古人。赖其有著述也。今子无一语之著述。后之人有谁知者。余笑曰古之君子。但务己实。不要人知。当世之不知。尚且不愠。况可念后人之不知乎。如我者本无为己之实。人之知不知。初非可论也。客曰吉人之辞寡。子之言。何似繁复耶。曰我非吉人。安能辞寡。且无己见。而只诵古人之说。务尽详悉。故自不觉其支蔓也。客笑曰固哉子志。听子之言而知子之志。愚生曩日之惑。今而解矣。不复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