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屯庵集卷之五 第 x 页
屯庵集卷之五(平山申 昉明远 著)
记
记
屯庵集卷之五 第 498H 页
 骊游记
骊游记乙酉九月。 朝家有 宁陵改莎之举。故事必大臣董其役。祖父奉 命当行。余平生闻清心,神勒之为胜观。而恨无因得见。欲随往一游。恐为人所指点。因就问于叔父。叔父曰。是无妨。纵有疑之者。不过为风流罪过也。余意遂定。与车起夫理行装。二十日朝。侍祖父。由兴仁门。过关帝庙。渡广津。暮投南汉开元寺。夜宿僧寮。有僧致惠者。来见曰。吾与沈公垂相识。今见子。如见沈公也。因问公垂安否。出松醪相待。味甚清。与之语。颇有韵致。非欺人化斋作恶业之类也。余甚爱之。惠亦喜我之能宽以律外。尽披心腹。二十一日晓。侍祖父出东门。向利川。致惠送别山门外数里许。颇有恋恋意。行一里回顾。尚立黄叶下望余行。余笑谓起夫曰。此释必不能做佛矣。起夫曰。何谓也。曰古佛。有三不宿桑下者。今此释。乃不能割去缘情如此。岂能做佛乎。起夫亦笑。是午。历省双岭,陶谷两先茔。入夜抵利川。饭后。与起夫及随行医官郑文进。同
屯庵集卷之五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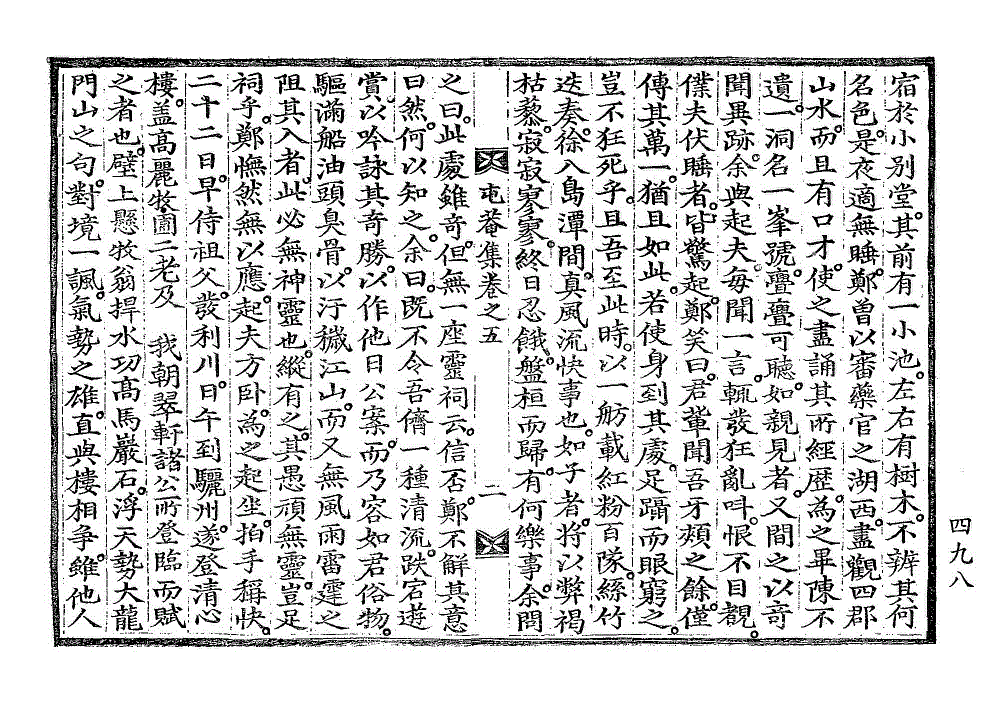 宿于小别堂。其前有一小池。左右有树木。不辨其何名色。是夜适无睡。郑曾以审药官之湖西。尽观四郡山水。而且有口才。使之尽诵其所经历。为之毕陈不遗。一洞名一峰号。亹亹可听。如亲见者。又间之以奇闻异迹。余与起夫。每闻一言。辄发狂乱叫。恨不目睹。仆夫伏睡者。皆惊起。郑笑曰。君辈闻吾牙颊之馀。仅传其万一。犹且如此。若使身到其处。足蹑而眼穷之。岂不狂死乎。且吾至此时。以一舫载红粉百队。丝竹迭奏。徐入岛潭间。真风流快事也。如子者。将以弊褐枯藜。寂寂寥寥。终日忍饿。盘桓而归。有何乐事。余问之曰。此处虽奇。但无一座灵祠云。信否。郑不解其意曰然。何以知之。余曰。既不令吾侪一种清流。跌宕游赏。以吟咏其奇胜。以作他日公案。而乃容如君俗物。驱满船油头臭骨。以污秽江山。而又无风雨雷霆之阻其入者。此必无神灵也。纵有之。其愚顽无灵。岂足祠乎。郑怃然无以应。起夫方卧。为之起坐。拍手称快。二十二日。早侍祖父。发利川。日午到骊州。遂登清心楼。盖高丽牧,圃二老及 我朝翠轩诸公所登临而赋之者也。壁上悬牧翁捍水功高马岩石。浮天势大龙门山之句。对境一讽。气势之雄。直与楼相争。虽他人
宿于小别堂。其前有一小池。左右有树木。不辨其何名色。是夜适无睡。郑曾以审药官之湖西。尽观四郡山水。而且有口才。使之尽诵其所经历。为之毕陈不遗。一洞名一峰号。亹亹可听。如亲见者。又间之以奇闻异迹。余与起夫。每闻一言。辄发狂乱叫。恨不目睹。仆夫伏睡者。皆惊起。郑笑曰。君辈闻吾牙颊之馀。仅传其万一。犹且如此。若使身到其处。足蹑而眼穷之。岂不狂死乎。且吾至此时。以一舫载红粉百队。丝竹迭奏。徐入岛潭间。真风流快事也。如子者。将以弊褐枯藜。寂寂寥寥。终日忍饿。盘桓而归。有何乐事。余问之曰。此处虽奇。但无一座灵祠云。信否。郑不解其意曰然。何以知之。余曰。既不令吾侪一种清流。跌宕游赏。以吟咏其奇胜。以作他日公案。而乃容如君俗物。驱满船油头臭骨。以污秽江山。而又无风雨雷霆之阻其入者。此必无神灵也。纵有之。其愚顽无灵。岂足祠乎。郑怃然无以应。起夫方卧。为之起坐。拍手称快。二十二日。早侍祖父。发利川。日午到骊州。遂登清心楼。盖高丽牧,圃二老及 我朝翠轩诸公所登临而赋之者也。壁上悬牧翁捍水功高马岩石。浮天势大龙门山之句。对境一讽。气势之雄。直与楼相争。虽他人屯庵集卷之五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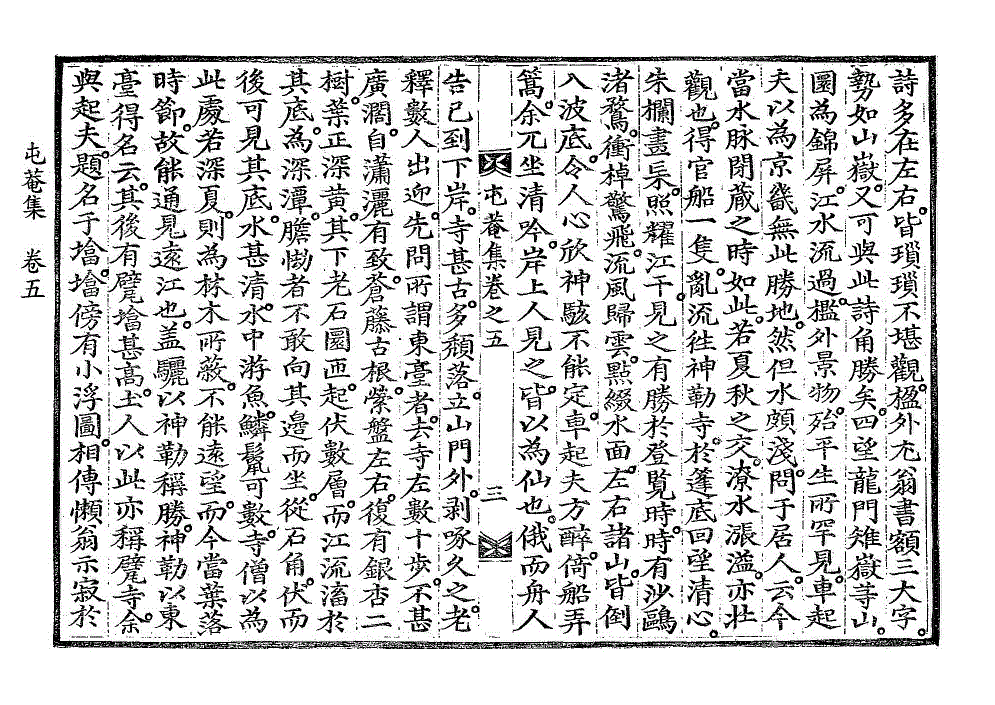 诗多在左右。皆琐琐不堪观。楹外尤翁书额三大字。势如山岳。又可与此诗角胜矣。四望龙门雉岳等山。圜为锦屏。江水流过。槛外景物。殆平生所罕见。车起夫以为京畿无此胜地。然但水颇浅。问于居人。云今当水脉闭藏之时如此。若夏秋之交。潦水涨溢。亦壮观也。得官船一只。乱流往神勒寺。于篷底回望清心。朱栏画杗。照耀江干。见之有胜于登览时。时有沙鸥渚鹜。冲棹惊飞。流风归云。点缀水面。左右诸山。皆倒入波底。令人心欣神骇不能定。车起夫方醉。倚船弄篙。余兀坐清吟。岸上人见之。皆以为仙也。俄而舟人告已到下岸。寺甚古。多颓落。立山门外。剥啄久之。老释数人出迎。先问所谓东台者。去寺左数十步。不甚广阔。自潇洒有致。苍藤古根。萦盘左右。复有银杏二树。叶正深黄。其下老石圜匝。起伏数层。而江流滀于其底。为深潭。胆㤼者不敢向其边而坐。从石角。伏而后可见其底。水甚清。水中游鱼。鳞鬣可数。寺僧以为此处若深夏。则为林木所蔽。不能远望。而今当叶落时节。故能通见远江也。盖骊以神勒称胜。神勒以东台得名云。其后有甓塔甚高。土人以此亦称甓寺。余与起夫。题名于塔。塔傍有小浮图。相传懒翁示寂于
诗多在左右。皆琐琐不堪观。楹外尤翁书额三大字。势如山岳。又可与此诗角胜矣。四望龙门雉岳等山。圜为锦屏。江水流过。槛外景物。殆平生所罕见。车起夫以为京畿无此胜地。然但水颇浅。问于居人。云今当水脉闭藏之时如此。若夏秋之交。潦水涨溢。亦壮观也。得官船一只。乱流往神勒寺。于篷底回望清心。朱栏画杗。照耀江干。见之有胜于登览时。时有沙鸥渚鹜。冲棹惊飞。流风归云。点缀水面。左右诸山。皆倒入波底。令人心欣神骇不能定。车起夫方醉。倚船弄篙。余兀坐清吟。岸上人见之。皆以为仙也。俄而舟人告已到下岸。寺甚古。多颓落。立山门外。剥啄久之。老释数人出迎。先问所谓东台者。去寺左数十步。不甚广阔。自潇洒有致。苍藤古根。萦盘左右。复有银杏二树。叶正深黄。其下老石圜匝。起伏数层。而江流滀于其底。为深潭。胆㤼者不敢向其边而坐。从石角。伏而后可见其底。水甚清。水中游鱼。鳞鬣可数。寺僧以为此处若深夏。则为林木所蔽。不能远望。而今当叶落时节。故能通见远江也。盖骊以神勒称胜。神勒以东台得名云。其后有甓塔甚高。土人以此亦称甓寺。余与起夫。题名于塔。塔傍有小浮图。相传懒翁示寂于屯庵集卷之五 第 499L 页
 此。而留头骨起浮图。稍左有碑。李崇仁作。今经三百年。字尚完好可读。稍后。又有碑。亦国初所立。列书当代发愿出力人姓氏。李名士。犹佞佛。作如此事。大书深刻。欲以示后。其时俗习可想。为之一叹。入门上大殿。有金像三躯。瓦炉纸灯。甚凄凉。有经数十卷。皆散缺。殿前有大石塔。刻画极巧。与汉城塔洞所有者。酷肖。意出于一手。寺僧言。壬辰倭乱。此寺被贼焚。塔独存。其上尚有烟煤。循廊。寻懒翁影殿。有懒翁,无学,指空三真画。皆劲峭目烂烂。如方视物而发慧音者。余谓起夫。此皆 国初魁杰士。虽遁迹沙门。其所作为。功业赫赫。非碌碌带革者比。且死留仪相。照耀后世。今吾辈。幸而识其面。今行所经江山不论。直此足偿脚债矣。因笑谈踟蹰。不觉日没。奴仆皆窃骂曰。是三介死像。有何好处。迟留不去。独不知吾等饥甚欲死乎。起夫微闻之。促余归船。还至骊郡。祖父已次 陵所。而吾辈不可从。方在寺时。因欲留宿。而意祖父尚留郡中归来。及还。始知极欲复往神勒。而已黄昏。且所得官船。已迎巡使去矣。懊恨移时。借村屋于清心楼下以宿。主人年老喜甚。明灯炊饭作款曲。俄而前后村舍。闻京客至。妇女数十人。来篱落外觇之。有顷
此。而留头骨起浮图。稍左有碑。李崇仁作。今经三百年。字尚完好可读。稍后。又有碑。亦国初所立。列书当代发愿出力人姓氏。李名士。犹佞佛。作如此事。大书深刻。欲以示后。其时俗习可想。为之一叹。入门上大殿。有金像三躯。瓦炉纸灯。甚凄凉。有经数十卷。皆散缺。殿前有大石塔。刻画极巧。与汉城塔洞所有者。酷肖。意出于一手。寺僧言。壬辰倭乱。此寺被贼焚。塔独存。其上尚有烟煤。循廊。寻懒翁影殿。有懒翁,无学,指空三真画。皆劲峭目烂烂。如方视物而发慧音者。余谓起夫。此皆 国初魁杰士。虽遁迹沙门。其所作为。功业赫赫。非碌碌带革者比。且死留仪相。照耀后世。今吾辈。幸而识其面。今行所经江山不论。直此足偿脚债矣。因笑谈踟蹰。不觉日没。奴仆皆窃骂曰。是三介死像。有何好处。迟留不去。独不知吾等饥甚欲死乎。起夫微闻之。促余归船。还至骊郡。祖父已次 陵所。而吾辈不可从。方在寺时。因欲留宿。而意祖父尚留郡中归来。及还。始知极欲复往神勒。而已黄昏。且所得官船。已迎巡使去矣。懊恨移时。借村屋于清心楼下以宿。主人年老喜甚。明灯炊饭作款曲。俄而前后村舍。闻京客至。妇女数十人。来篱落外觇之。有顷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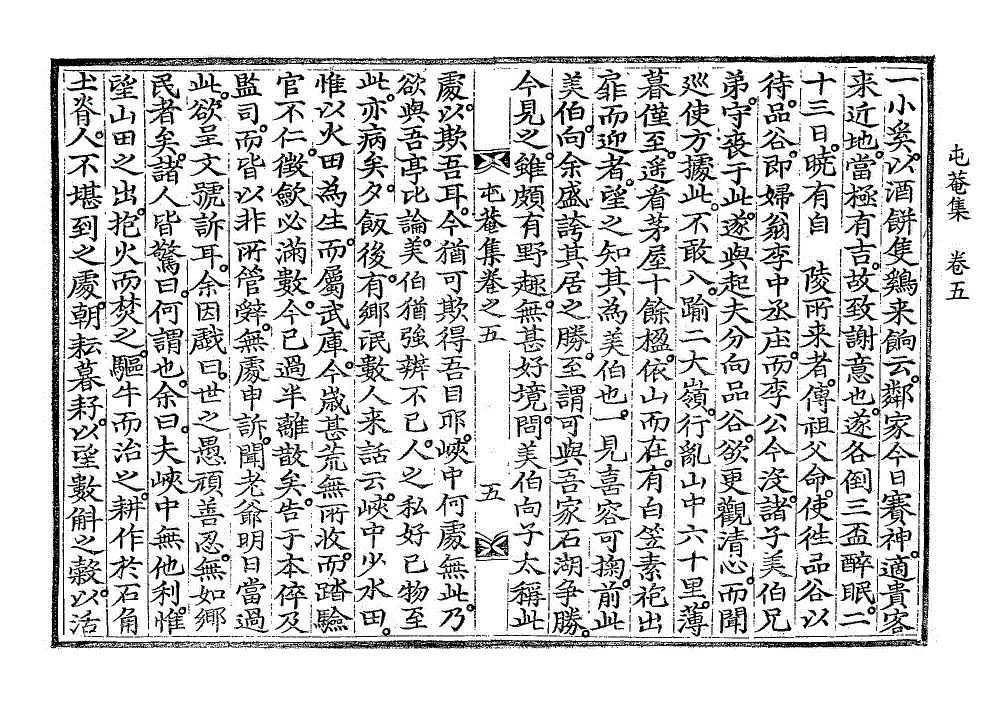 一小奚。以酒饼只鸡来饷云。邻家今日赛神。适贵客来近地。当极有吉。故致谢意也。遂各倒三杯醉眠。二十三日。晓有自 陵所来者。传祖父命。使往品谷以待。品谷。即妇翁李中丞庄。而李公今没。诸子美伯兄弟。守丧于此。遂与起夫分向品谷。欲更观清心。而闻巡使方据此。不敢入。踰二大岭。行乱山中六十里。薄暮仅至。遥看茅屋十馀楹。依山而在。有白笠素袍出扉而迎者。望之知其为美伯也。一见喜容可掬。前此美伯。向余盛誇其居之胜。至谓可与吾家石湖争胜。今见之。虽颇有野趣。无甚好境。问美伯向子太称此处。以欺吾耳。今犹可欺得吾目耶。峡中何处无此。乃欲与吾亭比论。美伯犹强辨不已。人之私好己物至此。亦病矣。夕饭后。有乡氓数人来话云。峡中少水田。惟以火田为生。而属武库。今岁甚荒无所收。而踏验官不仁。徵敛必满数。今已过半离散矣。告于本倅及监司。而皆以非所管辞。无处申诉。闻老爷明日当过此。欲呈文号诉耳。余因戏曰。世之愚顽善忍。无如乡民者矣。诸人皆惊曰。何谓也。余曰。夫峡中无他利。惟望山田之出。抱火而焚之。驱牛而治之。耕作于石角土脊。人不堪到之处。朝耘暮耔。以望数斛之谷。以活
一小奚。以酒饼只鸡来饷云。邻家今日赛神。适贵客来近地。当极有吉。故致谢意也。遂各倒三杯醉眠。二十三日。晓有自 陵所来者。传祖父命。使往品谷以待。品谷。即妇翁李中丞庄。而李公今没。诸子美伯兄弟。守丧于此。遂与起夫分向品谷。欲更观清心。而闻巡使方据此。不敢入。踰二大岭。行乱山中六十里。薄暮仅至。遥看茅屋十馀楹。依山而在。有白笠素袍出扉而迎者。望之知其为美伯也。一见喜容可掬。前此美伯。向余盛誇其居之胜。至谓可与吾家石湖争胜。今见之。虽颇有野趣。无甚好境。问美伯向子太称此处。以欺吾耳。今犹可欺得吾目耶。峡中何处无此。乃欲与吾亭比论。美伯犹强辨不已。人之私好己物至此。亦病矣。夕饭后。有乡氓数人来话云。峡中少水田。惟以火田为生。而属武库。今岁甚荒无所收。而踏验官不仁。徵敛必满数。今已过半离散矣。告于本倅及监司。而皆以非所管辞。无处申诉。闻老爷明日当过此。欲呈文号诉耳。余因戏曰。世之愚顽善忍。无如乡民者矣。诸人皆惊曰。何谓也。余曰。夫峡中无他利。惟望山田之出。抱火而焚之。驱牛而治之。耕作于石角土脊。人不堪到之处。朝耘暮耔。以望数斛之谷。以活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0L 页
 其妻子。而及其秋成。方欣然以为无忧。公婆相庆。于是乎贪官虐吏。从傍而攫之。使终岁勤苦者。不得一粒入口。嗷嗷田野。四顾无告。使如吾软肠人当之。将日夜怨泣。虽至哭死直不难。而君辈能全其躯壳。处若寻常。岂不顽然乎。诸人闻之。一时色惨然。不觉失声泣。正如小儿辈初仆地。不觉其痛。及长者扶起。而抚摩之。始乃啼号。正触其伤心处也。余心甚怜之。反悔其为此言也。二十四日。往拜岳君墓下。念南谷东床如昨日。而墓草已再宿矣。人事如何哉。饭后迎祖父。小留俟午炊。有自京来者传家报。叔父寄书曰。起夫必日须官醪三盏。应有好语。明远近来锐意为诗。只恨无处发奇思。今一得当清心楼。必有雄篇杰语。可与牧老,翠仙角争者云。余笑问起夫。此书于二人。皆有责。孰为尤难。起夫曰。子当难。余曰。不然。牧老,翠仙。东国之大家。吾之不相抗。固矣。虽叔父。未必责其必然也。饮官醪。赋好诗。寔容易也。叔父必以君为能之。而但君到处饮醪太过。未有一诗。是不能副其易者也。则君之藏拙。乃不如吾。岂不难哉。起夫亦笑。遂别美伯兄弟。向坤岩。中路拜燕尾茔下。暂登百仞台。水益清。石益癯。木叶皆赤。风吹飒飒有声。萧散吟啸。
其妻子。而及其秋成。方欣然以为无忧。公婆相庆。于是乎贪官虐吏。从傍而攫之。使终岁勤苦者。不得一粒入口。嗷嗷田野。四顾无告。使如吾软肠人当之。将日夜怨泣。虽至哭死直不难。而君辈能全其躯壳。处若寻常。岂不顽然乎。诸人闻之。一时色惨然。不觉失声泣。正如小儿辈初仆地。不觉其痛。及长者扶起。而抚摩之。始乃啼号。正触其伤心处也。余心甚怜之。反悔其为此言也。二十四日。往拜岳君墓下。念南谷东床如昨日。而墓草已再宿矣。人事如何哉。饭后迎祖父。小留俟午炊。有自京来者传家报。叔父寄书曰。起夫必日须官醪三盏。应有好语。明远近来锐意为诗。只恨无处发奇思。今一得当清心楼。必有雄篇杰语。可与牧老,翠仙角争者云。余笑问起夫。此书于二人。皆有责。孰为尤难。起夫曰。子当难。余曰。不然。牧老,翠仙。东国之大家。吾之不相抗。固矣。虽叔父。未必责其必然也。饮官醪。赋好诗。寔容易也。叔父必以君为能之。而但君到处饮醪太过。未有一诗。是不能副其易者也。则君之藏拙。乃不如吾。岂不难哉。起夫亦笑。遂别美伯兄弟。向坤岩。中路拜燕尾茔下。暂登百仞台。水益清。石益癯。木叶皆赤。风吹飒飒有声。萧散吟啸。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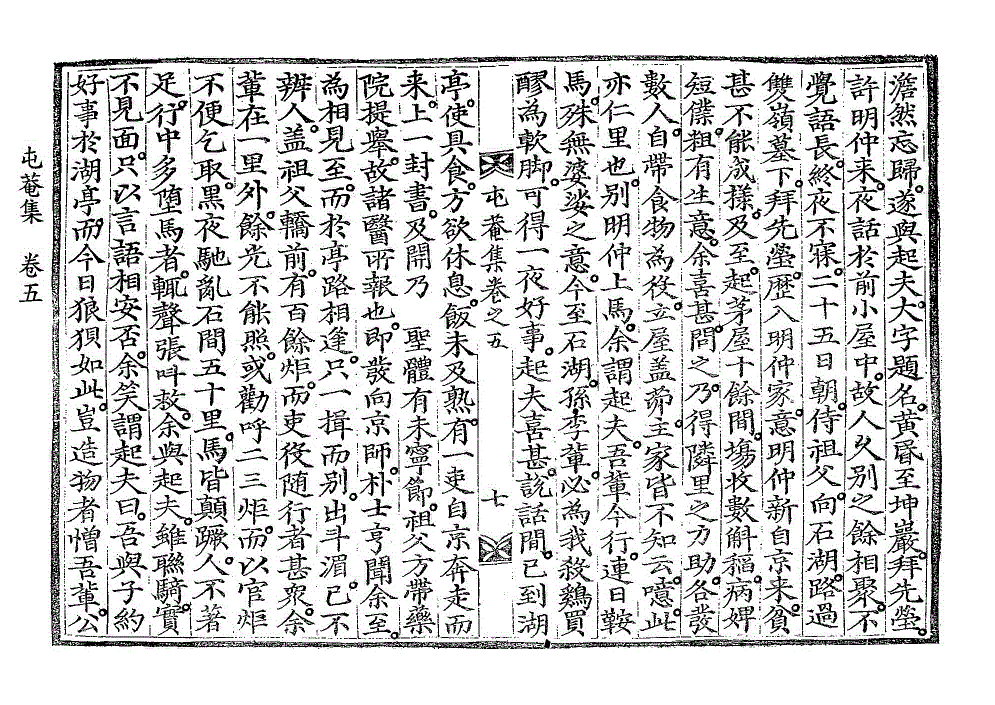 澹然忘归。遂与起夫。大字题名。黄昏至坤岩。拜先茔。许明仲来。夜话于前小屋中。故人久别之馀相聚。不觉语长。终夜不寐。二十五日朝。侍祖父。向石湖。路过双岭墓下。拜先茔。历入明仲家。意明仲新自京来。贫甚不能成㨾。及至。起茅屋十馀间。场收数斛稻。病婢短仆。粗有生意。余喜甚。问之。乃得邻里之力助。各发数人。自带食物为役。立屋盖茆。主家皆不知云。噫。此亦仁里也。别明仲上马。余谓起夫。吾辈今行。连日鞍马。殊无婆娑之意。今至石湖。孙,李辈。必为我杀鸡买醪为软脚。可得一夜好事。起夫喜甚。说话间。已到湖亭。使具食。方欲休息。饭未及熟。有一吏自京奔走而来。上一封书。及开乃 圣体有未宁节。祖父方带药院提举。故诸医所报也。即发向京师。朴士亨闻余至。为相见至。而于亭路相逢。只一揖而别。出斗湄。已不辨人。盖祖父轿前。有百馀炬。而吏役随行者甚众。余辈在一里外。馀光不能照。或劝呼二三炬。而以官炬不便乞取。黑夜驰乱石间五十里。马皆颠蹶。人不著足。行中多堕马者。辄声张叫救。余与起夫。虽联骑。实不见面。只以言语相安否。余笑谓起夫曰。吾与子约好事于湖亭。而今日狼狈如此。岂造物者憎吾辈。公
澹然忘归。遂与起夫。大字题名。黄昏至坤岩。拜先茔。许明仲来。夜话于前小屋中。故人久别之馀相聚。不觉语长。终夜不寐。二十五日朝。侍祖父。向石湖。路过双岭墓下。拜先茔。历入明仲家。意明仲新自京来。贫甚不能成㨾。及至。起茅屋十馀间。场收数斛稻。病婢短仆。粗有生意。余喜甚。问之。乃得邻里之力助。各发数人。自带食物为役。立屋盖茆。主家皆不知云。噫。此亦仁里也。别明仲上马。余谓起夫。吾辈今行。连日鞍马。殊无婆娑之意。今至石湖。孙,李辈。必为我杀鸡买醪为软脚。可得一夜好事。起夫喜甚。说话间。已到湖亭。使具食。方欲休息。饭未及熟。有一吏自京奔走而来。上一封书。及开乃 圣体有未宁节。祖父方带药院提举。故诸医所报也。即发向京师。朴士亨闻余至。为相见至。而于亭路相逢。只一揖而别。出斗湄。已不辨人。盖祖父轿前。有百馀炬。而吏役随行者甚众。余辈在一里外。馀光不能照。或劝呼二三炬。而以官炬不便乞取。黑夜驰乱石间五十里。马皆颠蹶。人不著足。行中多堕马者。辄声张叫救。余与起夫。虽联骑。实不见面。只以言语相安否。余笑谓起夫曰。吾与子约好事于湖亭。而今日狼狈如此。岂造物者憎吾辈。公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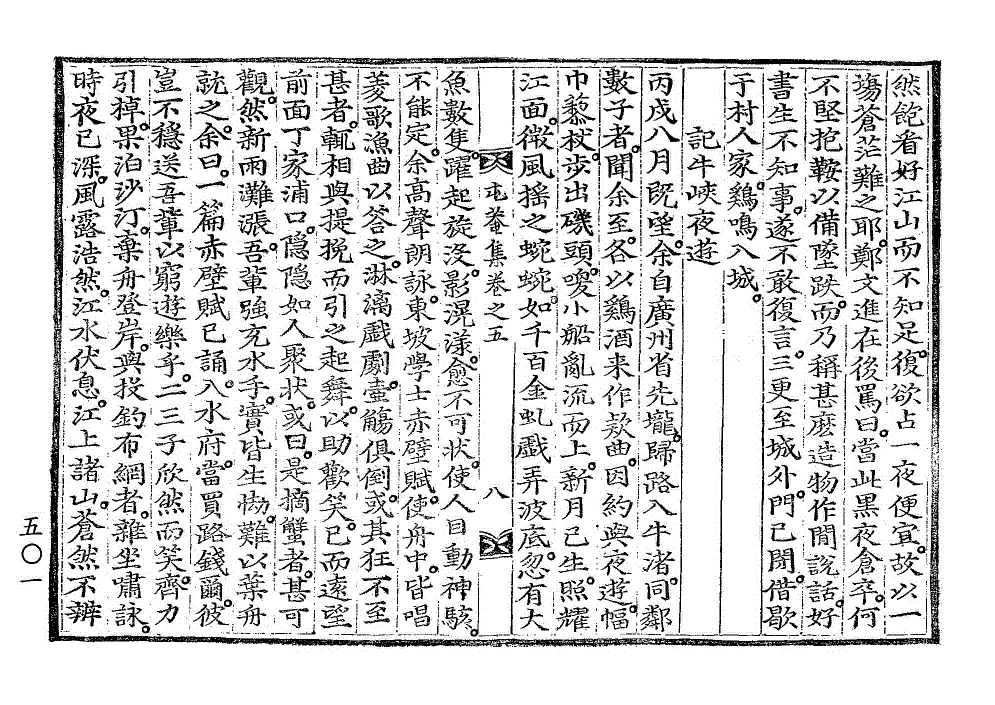 然饱看好江山而不知足。复欲占一夜便宜。故以一场苍茫难之耶。郑文进在后骂曰。当此黑夜仓卒。何不坚抱鞍以备坠跌。而乃称甚么造物作閒说话。好书生不知事。遂不敢复言。三更至城外。门已闭。借歇于村人家。鸡鸣入城。
然饱看好江山而不知足。复欲占一夜便宜。故以一场苍茫难之耶。郑文进在后骂曰。当此黑夜仓卒。何不坚抱鞍以备坠跌。而乃称甚么造物作閒说话。好书生不知事。遂不敢复言。三更至城外。门已闭。借歇于村人家。鸡鸣入城。记牛峡夜游
丙戌八月既望。余自广州省先垄。归路入牛渚。同邻数子者。闻余至。各以鸡酒来作款曲。因约与夜游。幅巾藜杖。步出矶头。唤小船乱流而上。新月已生。照耀江面。微风摇之蜿蜿。如千百金虬戏弄波底。忽有大鱼数只。跃起旋没。影滉漾。愈不可状。使人目动神骇。不能定。余高声朗咏。东坡学士赤壁赋。使舟中。皆唱菱歌渔曲以答之。淋漓戏剧。壶觞俱倒。或其狂不至甚者。辄相与提挽而引之起舞。以助欢笑。已而远望前面丁家浦口。隐隐如人聚状。或曰。是摘蟹者。甚可观。然新雨滩涨。吾辈强充水手。实皆生㤼。难以叶舟就之。余曰。一篇赤壁赋已诵。入水府。当买路钱尔。彼岂不稳送吾辈以穷游乐乎。二三子欣然而笑。齐力引棹。果泊沙汀。弃舟登岸。与投钓布网者。杂坐啸咏。时夜已深。风露浩然。江水伏息。江上诸山。苍然不辨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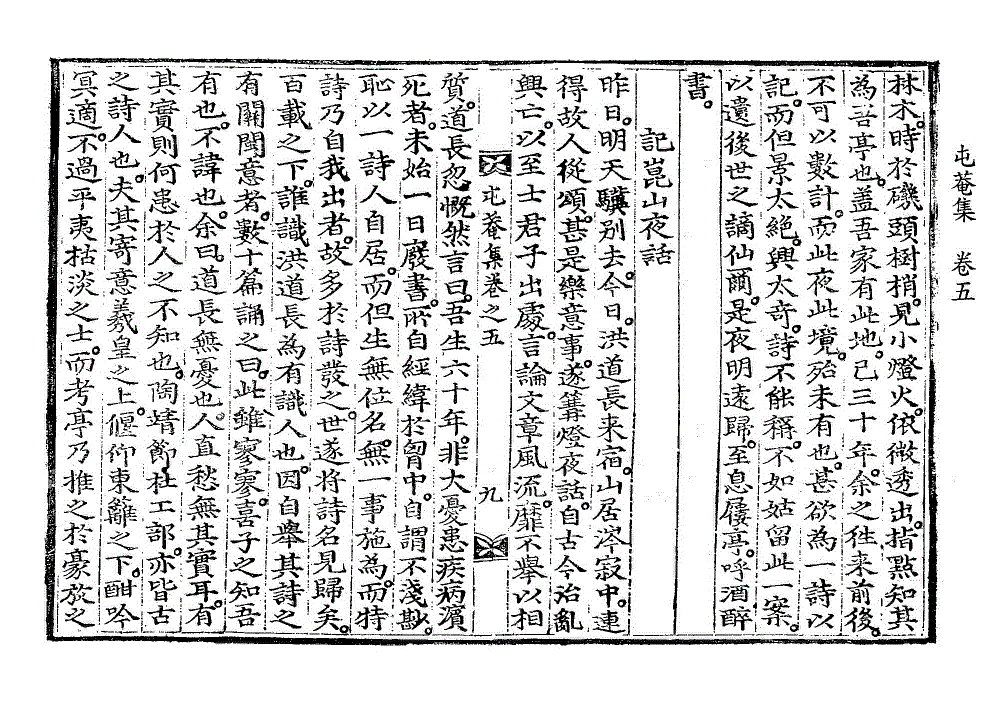 林木。时于矶头树梢。见小灯火。依微透出。指点知其为吾亭也。盖吾家有此地。已三十年。余之往来前后。不可以数计。而此夜此境。殆未有也。甚欲为一诗以记。而但景太绝。兴太奇。诗不能称。不如姑留此一案。以遗后世之谪仙尔。是夜明远归。至息屦亭。呼酒醉书。
林木。时于矶头树梢。见小灯火。依微透出。指点知其为吾亭也。盖吾家有此地。已三十年。余之往来前后。不可以数计。而此夜此境。殆未有也。甚欲为一诗以记。而但景太绝。兴太奇。诗不能称。不如姑留此一案。以遗后世之谪仙尔。是夜明远归。至息屦亭。呼酒醉书。记昆山夜话
昨日。明天骥别去。今日。洪道长来宿。山居涔寂中。连得故人从颂。甚是乐意事。遂篝灯夜话。自古今治乱兴亡。以至士君子出处。言论文章风流。靡不举以相质。道长忽慨然言曰。吾生六十年。非大忧患疾病滨死者。未始一日废书。所自经纬于胸中。自谓不浅鲜。耻以一诗人自居。而但生无位名。无一事施为。而特诗乃自我出者。故多于诗发之。世遂将诗名见归矣。百载之下。谁识洪道长为有识人也。因自举其诗之有关闽意者。数十篇诵之曰。此虽寥寥。喜子之知吾有也。不讳也。余曰。道长无忧也。人直愁无其实耳。有其实则何患于人之不知也。陶靖节,杜工部。亦皆古之诗人也。夫其寄意羲皇之上。偃仰东篱之下。酣吟冥适。不过平夷枯淡之士。而考亭乃推之于豪放之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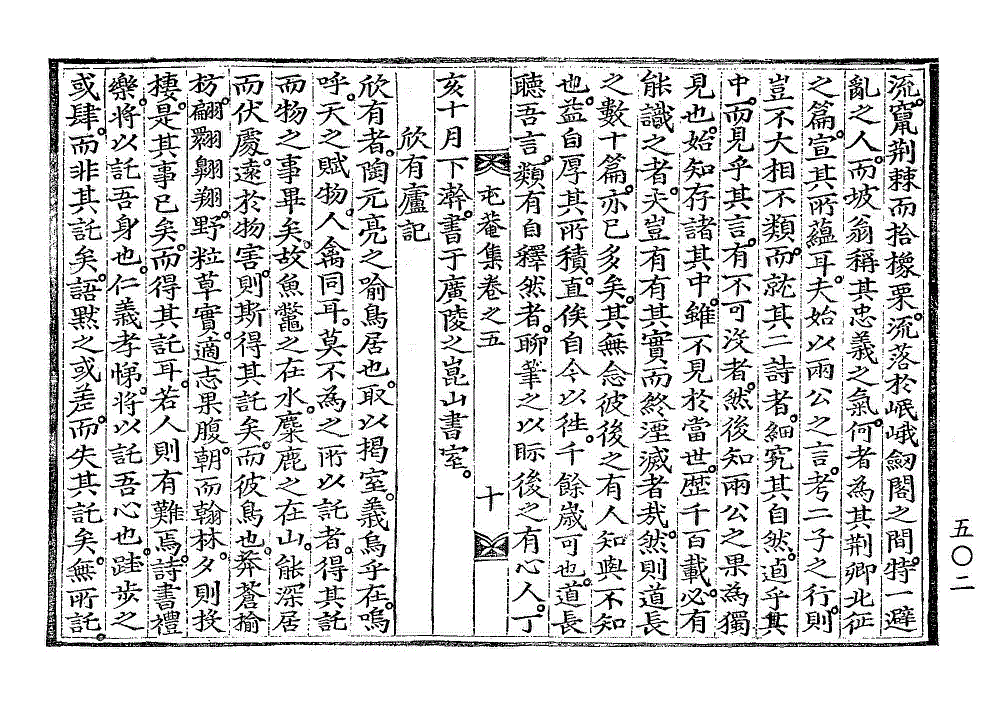 流。窜荆棘而拾橡栗。流落于岷峨剑阁之间。特一避乱之人。而坡翁称其忠义之气。何者为其荆卿北征之篇。宣其所蕴耳。夫始以两公之言。考二子之行。则岂不大相不类。而就其二诗者。细究其自然。逌乎其中。而见乎其言。有不可没者。然后知两公之果为独见也。始知存诸其中。虽不见于当世。历千百载。必有能识之者。夫岂有有其实而终湮灭者哉。然则道长之数十篇。亦已多矣。其无念彼后之有人知与不知也。益自厚其所积。直俟自今以往。千馀岁可也。道长听吾言。类有自释然者。聊笔之以视后之有心人。丁亥十月下浣。书于广陵之昆山书室。
流。窜荆棘而拾橡栗。流落于岷峨剑阁之间。特一避乱之人。而坡翁称其忠义之气。何者为其荆卿北征之篇。宣其所蕴耳。夫始以两公之言。考二子之行。则岂不大相不类。而就其二诗者。细究其自然。逌乎其中。而见乎其言。有不可没者。然后知两公之果为独见也。始知存诸其中。虽不见于当世。历千百载。必有能识之者。夫岂有有其实而终湮灭者哉。然则道长之数十篇。亦已多矣。其无念彼后之有人知与不知也。益自厚其所积。直俟自今以往。千馀岁可也。道长听吾言。类有自释然者。聊笔之以视后之有心人。丁亥十月下浣。书于广陵之昆山书室。欣有庐记
欣有者。陶元亮之喻鸟居也。取以揭室。义乌乎在。呜呼。天之赋物。人禽同耳。莫不为之所以托者。得其托而物之事毕矣。故鱼鳖之在水。麋鹿之在山。能深居而伏处。远于物害。则斯得其托矣。而彼鸟也。莽苍榆枋。翩翾翱翔。野粒草实。适志果腹。朝而翰林。夕则投栖。是其事已矣。而得其托耳。若人则有难焉。诗书礼乐。将以托吾身也。仁义孝悌。将以托吾心也。跬步之或肆。而非其托矣。语默之或差。而失其托矣。无所托。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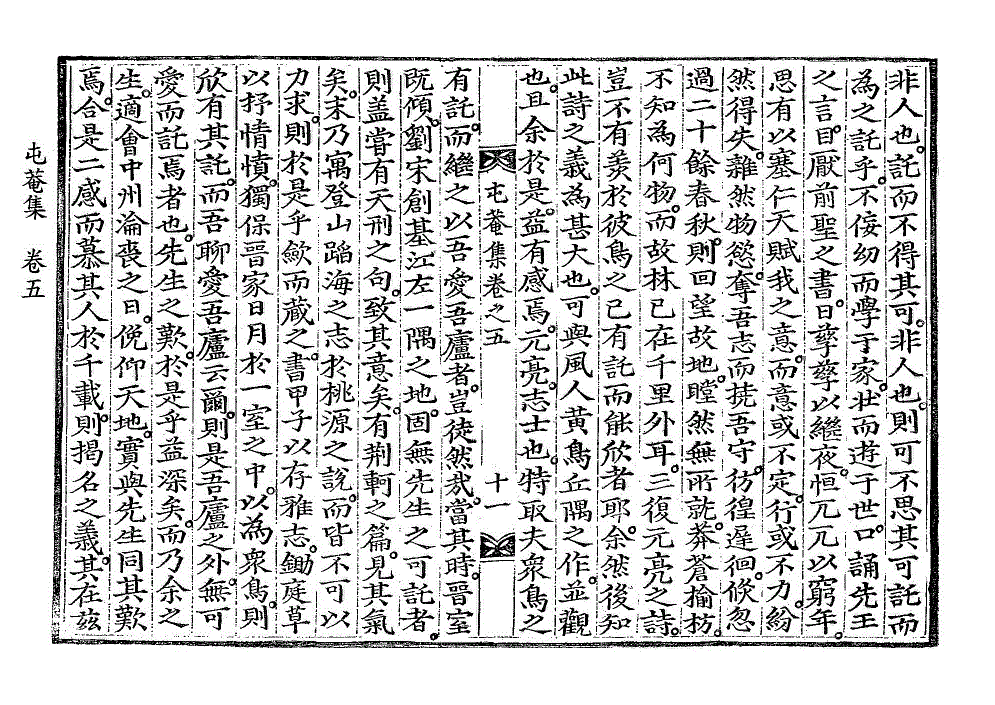 非人也。托而不得其可。非人也。则可不思其可托而为之托乎。不佞幼而学于家。壮而游于世。口诵先王之言。目厌前圣之书。日孳孳以继夜。恒兀兀以穷年。思有以塞仁天赋我之意。而意或不定。行或不力。纷然得失。杂然物欲。夺吾志而挠吾守。彷徨迟徊。倏忽过二十馀春秋。则回望故地。瞠然无所就。莽苍榆枋。不知为何物。而故林已在千里外耳。三复元亮之诗。岂不有羡于彼鸟之已有托而能欣者耶。余然后知此诗之义为甚大也。可与风人黄鸟丘隅之作。并观也。且余于是。益有感焉。元亮。志士也。特取夫众鸟之有托。而继之以吾爱吾庐者。岂徒然哉。当其时。晋室既倾。刘宋创基江左一隅之地。固无先生之可托者。则盖尝有天刑之句。致其意矣。有荆轲之篇。见其气矣。末乃寓登山蹈海之志于桃源之说。而皆不可以力求。则于是乎敛而藏之。书甲子以存雅志。锄庭草以抒情愤。独保晋家日月于一室之中。以为众鸟。则欣有其托。而吾聊爱吾庐云尔。则是吾庐之外。无可爱而托焉者也。先生之叹。于是乎益深矣。而乃余之生。适会中州沦丧之日。俛仰天地。实与先生同其叹焉。合是二感而慕其人于千载。则揭名之义。其在玆
非人也。托而不得其可。非人也。则可不思其可托而为之托乎。不佞幼而学于家。壮而游于世。口诵先王之言。目厌前圣之书。日孳孳以继夜。恒兀兀以穷年。思有以塞仁天赋我之意。而意或不定。行或不力。纷然得失。杂然物欲。夺吾志而挠吾守。彷徨迟徊。倏忽过二十馀春秋。则回望故地。瞠然无所就。莽苍榆枋。不知为何物。而故林已在千里外耳。三复元亮之诗。岂不有羡于彼鸟之已有托而能欣者耶。余然后知此诗之义为甚大也。可与风人黄鸟丘隅之作。并观也。且余于是。益有感焉。元亮。志士也。特取夫众鸟之有托。而继之以吾爱吾庐者。岂徒然哉。当其时。晋室既倾。刘宋创基江左一隅之地。固无先生之可托者。则盖尝有天刑之句。致其意矣。有荆轲之篇。见其气矣。末乃寓登山蹈海之志于桃源之说。而皆不可以力求。则于是乎敛而藏之。书甲子以存雅志。锄庭草以抒情愤。独保晋家日月于一室之中。以为众鸟。则欣有其托。而吾聊爱吾庐云尔。则是吾庐之外。无可爱而托焉者也。先生之叹。于是乎益深矣。而乃余之生。适会中州沦丧之日。俛仰天地。实与先生同其叹焉。合是二感而慕其人于千载。则揭名之义。其在玆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3L 页
 欤。其在玆欤。嗟乎。其孰能知之。
欤。其在玆欤。嗟乎。其孰能知之。韦岩精舍记
出东城二十里。有山为峨嵯。有里为忘忧。自峨嵯延一麓下忘忧者。为申氏之坟山焉。负麓而堂者。曰韦岩精舍。即吾先祖大冢宰文节公所尝卜筑者。盖取名于室右大石。窃寓古人佩韦之义。而岁久颓圮。先王父大丞相平川公。仍其基而新之者也。文节公弱冠。阐大科。秉直道。辅人主。将欲使世三代。而俗熙皞焉。时则有静庵赵文正公实与之。志同道合。相左右焉。其为冢宰也。激浊扬清。辟正路。杜倖门。深为群小人所盱睢。顾不恤也。逮夫北门之祸作。静庵诸公。一时并刘。维时文节公。危及之而适免焉。然自是摈斥。徊徨于散地以终焉。盖时固不欲公在朝。而公亦无意于当世矣。敛志全名。确然有守东冈之志。佩韦之戒。于是乎作。而是堂也实肇创焉。故先王父最尝眷眷于玆。既夷而复营之。既营而复时至焉。至于晚年。盖有终焉之志。而未几即捐世。痛哉。然不肖幸而及长于先王父之世。侍起居于玆地。为有年焉。则盖尝奉朝夕之训辞矣。以为人之于世。可慕者多矣。学以慕孔孟焉。仕以慕将相焉。家而慕富积焉。处而慕旷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4H 页
 散焉。慕则思有之。然乃子孙之于祖先。其慕也益切。语笑之或同而则为荣焉。嗜好之适类而则为幸焉。况如文节公之德业文彩。清名直节。将国人而慕之矣。况在子孙之列者乎。今余所以复置斯堂。而名以旧称者。俾后世子孙。睹物而起敬。抚迹而兴怀。追而慕之。勉而继之。得无忝于先烈也。然文节公之为世所尊。至今称焉者有二焉。之德也。之位也。为子孙者。苟能克自树立。羽仪朝廷。显于时而扬于先。以企夫文节公之德与位则固美矣。虽不然。能自砥励名行。力于文学。克有成就。不愧为文节公之孙。则虽未有其位。是亦可谓无坠矣。余将与之矣。若徒事乎名利。淫乎富贵。进无可观之节。退无可述之行。纵使名嵬赫而位崇高。余则不与。非但余之不与。抑亦文节公之所不与乐也。余既治斯堂。将揭是以视来人。顾老不欲多言。汝其志之。不肖再拜而默记乎中。而不敢文矣。今先王父之训。不可得以复承。而岁已五六易矣。若不肖躬受教而无言也。则其在千百载之后。将何徵乎。于是涕泣而次先王父之训惟谨。不敢妄有所加。呜呼。先王父德尊位隆。名著事显。诚有光于文节公。而犹以为德由我勉。而位在外求。其所以训诸
散焉。慕则思有之。然乃子孙之于祖先。其慕也益切。语笑之或同而则为荣焉。嗜好之适类而则为幸焉。况如文节公之德业文彩。清名直节。将国人而慕之矣。况在子孙之列者乎。今余所以复置斯堂。而名以旧称者。俾后世子孙。睹物而起敬。抚迹而兴怀。追而慕之。勉而继之。得无忝于先烈也。然文节公之为世所尊。至今称焉者有二焉。之德也。之位也。为子孙者。苟能克自树立。羽仪朝廷。显于时而扬于先。以企夫文节公之德与位则固美矣。虽不然。能自砥励名行。力于文学。克有成就。不愧为文节公之孙。则虽未有其位。是亦可谓无坠矣。余将与之矣。若徒事乎名利。淫乎富贵。进无可观之节。退无可述之行。纵使名嵬赫而位崇高。余则不与。非但余之不与。抑亦文节公之所不与乐也。余既治斯堂。将揭是以视来人。顾老不欲多言。汝其志之。不肖再拜而默记乎中。而不敢文矣。今先王父之训。不可得以复承。而岁已五六易矣。若不肖躬受教而无言也。则其在千百载之后。将何徵乎。于是涕泣而次先王父之训惟谨。不敢妄有所加。呜呼。先王父德尊位隆。名著事显。诚有光于文节公。而犹以为德由我勉。而位在外求。其所以训诸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4L 页
 后也。则曰无以位而以德。可见其责之重而望之深矣。凡为后裔。有不克佩服斯训。用自奋发。徒生浪死。坠落先烈。则将何颜以登斯堂乎。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后也。则曰无以位而以德。可见其责之重而望之深矣。凡为后裔。有不克佩服斯训。用自奋发。徒生浪死。坠落先烈。则将何颜以登斯堂乎。可不惧哉。可不惧哉。屯庵集卷之五(平山申 昉明远 著)
题跋
书秦始皇本纪后
始皇二十六年。下制除谥法。自称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呜呼。秦之亡。形于是矣。世人徒见其奉玺轵道之为秦亡。而不知其已亡于此诏也。岂不惑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一姓之所以享其利者。乃有德者奉天恤民之公器也。其位也实天与民主之。其所为。一违乎天拂乎民。皆不得以有之矣。为人君者。将自惧其身之或违于天而拂于民也。其可以自私于千万世而不失乎。昔尧以天下传舜。舜以传禹。夫若彼朱与均者。皆可足以奉天命恤民。庶为继世之君。则尧舜独以何心。必夺诸子而与人乎。此人情之所不为也。尧舜之德入人肌。如雨之润。如春之养。至使民皞皞然不知其力。而及知其子之不足以膺天民之责。则乃舍之而择贤。然犹未敢专也。试之民而荐之天而后与之。其慄慄乎天民之间。不敢自用也如此。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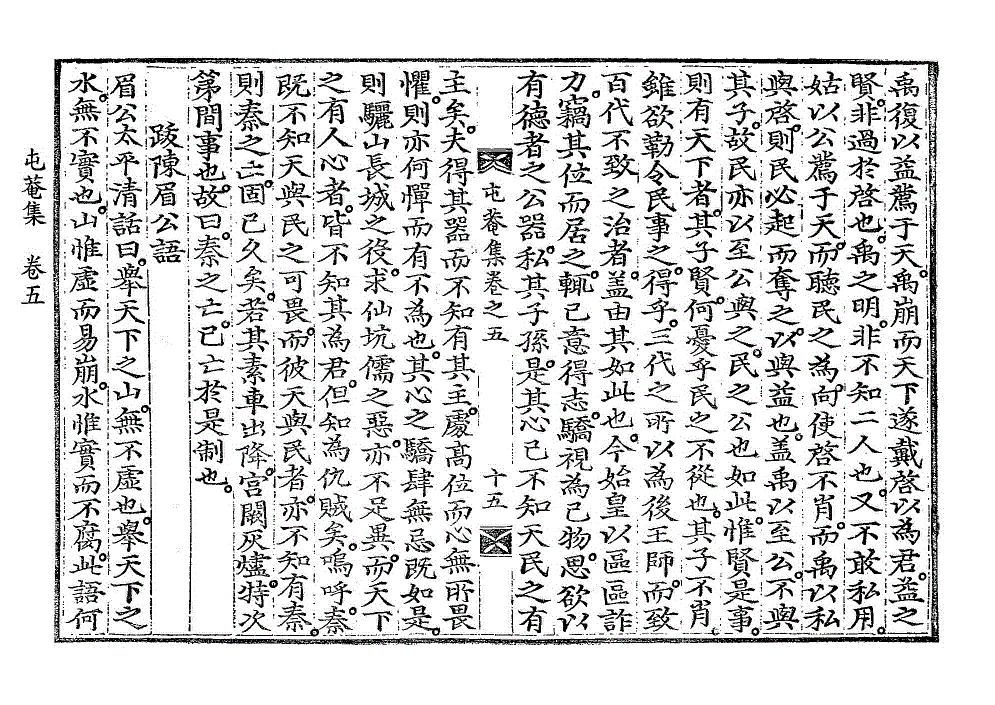 禹复以益荐于天。禹崩而天下遂戴启以为君。益之贤。非过于启也。禹之明。非不知二人也。又不敢私用。姑以公荐于天。而听民之为。向使启不肖。而禹以私与启。则民必起而夺之。以与益也。盖禹以至公。不与其子。故民亦以至公与之。民之公也如此。惟贤是事。则有天下者。其子贤。何忧乎民之不从也。其子不肖。虽欲勒令民事之。得乎。三代之所以为后王师。而致百代不致之治者。盖由其如此也。今始皇以区区诈力。窃其位而居之。辄己意得志。骄视为己物。思欲以有德者之公器。私其子孙。是其心已不知天民之有主矣。夫得其器而不知有其主。处高位而心无所畏惧。则亦何惮而有不为也。其心之骄肆无忌既如是。则骊山长城之役。求仙坑儒之恶。亦不足异。而天下之有人心者。皆不知其为君。但知为仇贼矣。呜呼。秦既不知天与民之可畏。而彼天与民者。亦不知有秦。则秦之亡。固已久矣。若其素车出降。宫阙灰烬。特次第间事也。故曰。秦之亡。已亡于是制也。
禹复以益荐于天。禹崩而天下遂戴启以为君。益之贤。非过于启也。禹之明。非不知二人也。又不敢私用。姑以公荐于天。而听民之为。向使启不肖。而禹以私与启。则民必起而夺之。以与益也。盖禹以至公。不与其子。故民亦以至公与之。民之公也如此。惟贤是事。则有天下者。其子贤。何忧乎民之不从也。其子不肖。虽欲勒令民事之。得乎。三代之所以为后王师。而致百代不致之治者。盖由其如此也。今始皇以区区诈力。窃其位而居之。辄己意得志。骄视为己物。思欲以有德者之公器。私其子孙。是其心已不知天民之有主矣。夫得其器而不知有其主。处高位而心无所畏惧。则亦何惮而有不为也。其心之骄肆无忌既如是。则骊山长城之役。求仙坑儒之恶。亦不足异。而天下之有人心者。皆不知其为君。但知为仇贼矣。呜呼。秦既不知天与民之可畏。而彼天与民者。亦不知有秦。则秦之亡。固已久矣。若其素车出降。宫阙灰烬。特次第间事也。故曰。秦之亡。已亡于是制也。跋陈眉公语
眉公太平清话曰。举天下之山。无不虚也。举天下之水。无不实也。山惟虚而易崩。水惟实而不腐。此语何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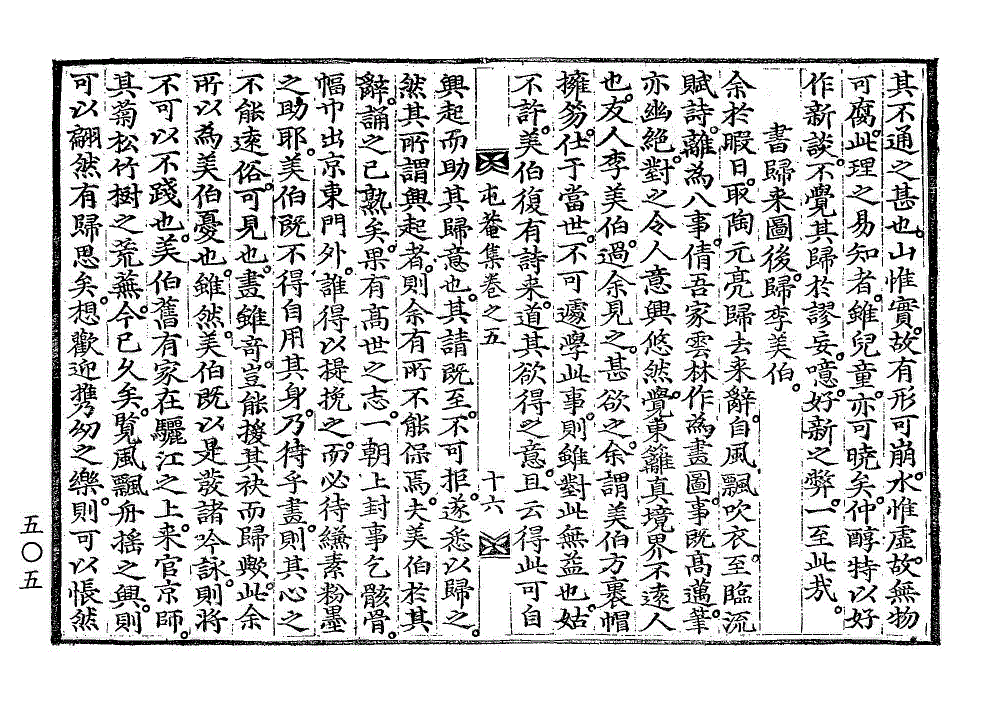 其不通之甚也。山惟实。故有形可崩。水惟虚。故无物可腐。此理之易知者。虽儿童。亦可晓矣。仲醇特以好作新谈。不觉其归于谬妄。噫。好新之弊。一至此哉。
其不通之甚也。山惟实。故有形可崩。水惟虚。故无物可腐。此理之易知者。虽儿童。亦可晓矣。仲醇特以好作新谈。不觉其归于谬妄。噫。好新之弊。一至此哉。书归来图后。归李美伯。
余于暇日。取陶元亮归去来辞。自风飘吹衣。至临流赋诗。离为八事。倩吾家云林作为画图。事既高迈。笔亦幽绝。对之令人意兴悠然。觉东篱真境界不远人也。友人李美伯。过余见之。甚欲之。余谓美伯方裹帽拥笏。仕于当世。不可遽学此事。则虽对此无益也。姑不许。美伯复有诗来。道其欲得之意。且云得此可自兴起而助其归意也。其请既至。不可拒。遂悉以归之。然其所谓兴起者。则余有所不能保焉。夫美伯于其辞。诵之已熟矣。果有高世之志。一朝上封事乞骸骨。幅巾出京东门外。谁得以提挽之。而必待缣素粉墨之助耶。美伯既不得自用其身。乃待乎画。则其心之不能远俗。可见也。画虽奇。岂能援其袂而归欤。此余所以为美伯忧也。虽然。美伯既以是发诸吟咏。则将不可以不践也。美伯旧有家在骊江之上。来官京师。其菊松竹树之荒芜。今已久矣。览风飘舟摇之兴。则可以翩然有归思矣。想欢迎携幼之乐。则可以怅然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6H 页
 怀故宇矣。去舆马宾从之盛。而为巾车之游。云鸟之观。远簿牍应接之烦。而为亲戚之话。临流之閒。使西畴之间。有归耕之人。南牖之下。著寄傲之客。则可以为天地间大自在人。而无愧于对此图矣。向余所以忧美伯者。亦可以尽无也。美伯果能办此也。余虽病。可以一棹溯骊水而上。与美伯为刘柴桑庞参军之游。以继斜川故事可矣。如其未也。余将执此为左契。责其实于美伯矣。未知美伯将何以堪之。聊书以问之。
怀故宇矣。去舆马宾从之盛。而为巾车之游。云鸟之观。远簿牍应接之烦。而为亲戚之话。临流之閒。使西畴之间。有归耕之人。南牖之下。著寄傲之客。则可以为天地间大自在人。而无愧于对此图矣。向余所以忧美伯者。亦可以尽无也。美伯果能办此也。余虽病。可以一棹溯骊水而上。与美伯为刘柴桑庞参军之游。以继斜川故事可矣。如其未也。余将执此为左契。责其实于美伯矣。未知美伯将何以堪之。聊书以问之。题家藏兰亭帖后
兰亭之流落人间者。余阅数百千纸。终未见若此本能真有右军手脚也。当以此本定为世本之第一矣。然尝读坡翁题识。其时去晋。视今为近。犹以世无真本。叹后生之所见愈微愈疏。今距此翁。且历累多百年矣。则此本虽善。安知非当日之下品哉。又未知今后而生者。当复何观哉。时代渐下。自天地孕育之气。已不能无少杀。遂至人物万类。新者辄不如故。况此枣木传刻每一翻。辄失一顿真气者哉。余之叹。不独为兰亭者也。戊子元月上日。明远书于愉春轩。时夜三鼓。群动已息。有怀如山。无可与语者。怅然久之。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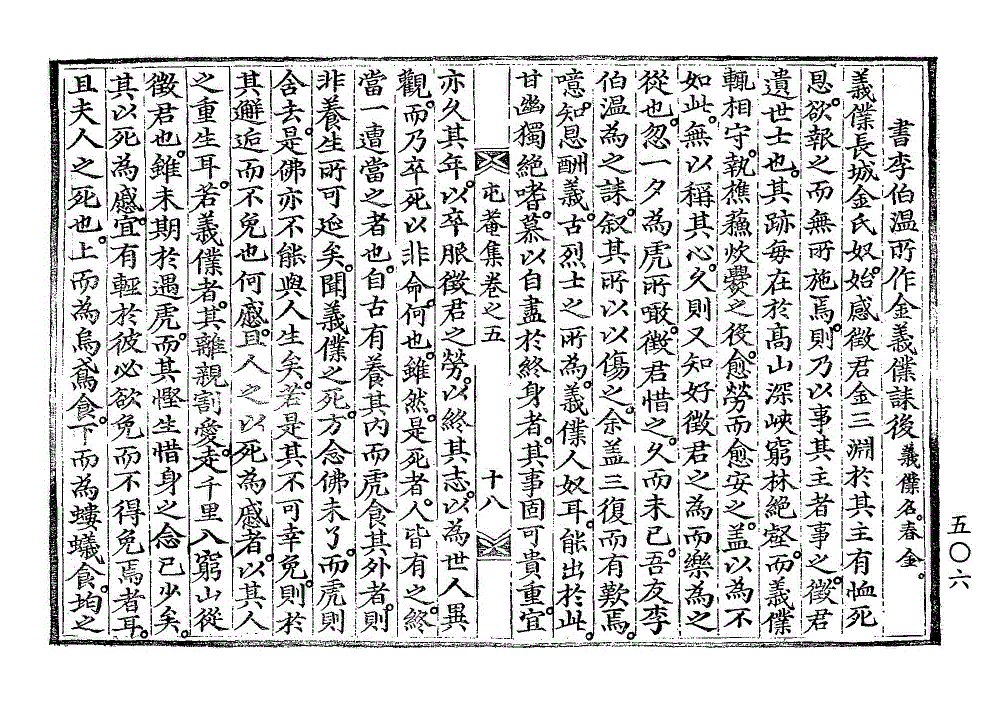 书李伯温所作金义仆诔后(义仆名。春金。)
书李伯温所作金义仆诔后(义仆名。春金。)义仆长城金氏奴。始感徵君金三渊于其主有恤死恩。欲报之而无所施焉。则乃以事其主者事之。徵君遗世士也。其迹每在于高山深峡穷林绝壑。而义仆辄相守。执樵苏炊爨之役。愈劳而愈安之。盖以为不如此。无以称其心。久则又知好徵君之为而乐为之从也。忽一夕为虎所啖。徵君惜之。久而未已。吾友李伯温为之诔。叙其所以以伤之。余盖三复而有叹焉。噫。知恩酬义。古烈士之所为。义仆人奴耳。能出于此。甘幽独绝嗜。慕以自尽于终身者。其事固可贵重。宜亦久其年。以卒服徵君之劳。以终其志。以为世人异观。而乃卒死以非命。何也。虽然。是死者。人皆有之。终当一遭当之者也。自古有养其内而虎食其外者。则非养生所可延矣。闻义仆之死。方念佛未了。而虎则含去。是佛亦不能与人生矣。若是其不可幸免。则于其邂逅而不免也何戚。且人之以死为戚者。以其人之重生耳。若义仆者。其离亲割爱。走千里入穷山从徵君也。虽未期于遇虎。而其悭生惜身之念已少矣。其以死为戚。宜有轻于彼必欲免而不得免焉者耳。且夫人之死也。上而为乌鸢食。下而为蝼蚁食。均之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7H 页
 一无此气。身则无有矣。佛家又必茶毗之。是又以为幻妄不足存也。然则是葬之于虎口者。其视死闺闼之奥。斸文章之材。裹漆絮。列明旌。引槥輀。姑为耳目观者。安见其益毒乎。且之人也。能念佛则是有志于学佛矣。佛固有以肉喂猛兽者。是其死无亦出于此法耶。然此皆悯义仆之死而为之解耳。若义仆之心。只为是为其主而报恩也者。而其生也知尽其力。其死也无憾而已矣。是可书也。丙申岁冬日。书。
一无此气。身则无有矣。佛家又必茶毗之。是又以为幻妄不足存也。然则是葬之于虎口者。其视死闺闼之奥。斸文章之材。裹漆絮。列明旌。引槥輀。姑为耳目观者。安见其益毒乎。且之人也。能念佛则是有志于学佛矣。佛固有以肉喂猛兽者。是其死无亦出于此法耶。然此皆悯义仆之死而为之解耳。若义仆之心。只为是为其主而报恩也者。而其生也知尽其力。其死也无憾而已矣。是可书也。丙申岁冬日。书。题姜翠岩(锡朋)遗墨后
余与翠岩姜公。生并世。且慕之。不及一见而公殁。余过也。今就郑元猷所藏墨迹一帖。因其心画。而有得于其为人之髣髴。盖为一味淳古真朴。不为便巧媚世人眼。其用心固不苟矣。余益敬之。此岂可以书言哉。仍念公。即我外王考朴文纯公之门人。记十年前。世有乱经之变。公为文纯公。封章辨之。有曰。是所谓以夫子之道害夫子。其辞截严。余每诵之。噫。世衰风夷。师友道废。知公之义者。盖少矣。向之所抠衣服勤者。而其势利不足以誇耀。则有羞而讳之者。甚或关射羿之弓而向之矣。其视公何如也。凡为后学者。苟能追公之义。而思不作去金者之罪人。则今日世界。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7L 页
 庶不为今日世界也。故特书以表之。若其学术之醇正。践履之坚笃。千载之下。必不以其穷而废之矣。余何言。己亥季夏下浣。书于翰苑直庐。
庶不为今日世界也。故特书以表之。若其学术之醇正。践履之坚笃。千载之下。必不以其穷而废之矣。余何言。己亥季夏下浣。书于翰苑直庐。屯庵集卷之五(平山申 昉明远 著)
杂著
东坡得志。其害甚于荆公论。(科作。)
论曰。君子有观人之术。不先察乎其迹。而必察乎其心。不徒究乎其外。而必究乎其内。则斯可谓得之矣。在昔赵宋之世。苏,王之学。行于天下。而王氏之学。已试于神宗之时。生民受其害。国家受其病。当世之士大夫。莫不知其为非。而于苏氏之学。犹未能深识。靡然一趍。有师而宗之者。有扶而翊之者。而独我考亭朱夫子极言而痛辨之。以为若得志。其害甚于荆公。夫泛论之。则苏氏之学。其文章之发乎外者。无非论道谈理之说。行事之见于迹者。无非爱君忧国之事。则其视王氏之学。岂不大相过之。而考亭之言。乃至于此。何哉。呜呼。此向所谓得观人之术。而明乎心迹内外者也。彼王氏之初。亦岂不善人哉。廉洁以文其身。刻苦以饰其行。孝友闻于世。政事称于朝。以此而欺人。以此而干君。何往而不得哉。及其身登庙堂。手执国命。则毒害之政。遍于天下。而国随而乱矣。是果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8H 页
 其饰于外者。不足而然欤。抑其心有所偏系拗滞而然耶。由此观之。苏氏之学。亦可从而论之矣。今夫苏氏者。果何人哉。主老佛申韩之学。而文之以孔孟。挟纵横捭阖之术。而假之以仁义。高其眼。大其言。眩一世之耳目。苟非克察其心术之隐微。克究其学问之谬戾者。孰得以辨之哉。使此人得其位行其道。则其害人国家。可胜言哉。且夫今之罪王氏者。以其兴兵开衅。以伤国脉。而苏氏之初年。亦尝进用兵之说矣。今之罪王氏者。以其造法取利。以病生民。而苏氏之初年。亦尝进生财之说矣。及见王氏之为此事。遂致狼狈。乃一反前日用兵之说。以攻王氏兴兵之害。一反前日生财之说。以攻王氏取利之弊。此果其学贤于王氏而然欤。夫王氏之心。犹苏氏之心。苏氏之学。犹王氏之学也。心异其用。而不得其正则同。学异其致。而可以误国则同。然则荆公。特毕露手脚之子瞻也。子瞻即未试其术之荆公也。其得位也。乃王氏之不幸也。其不得位也。乃苏氏之幸也。然而王氏之学。如断鹌鹑之狱。制字说之书。皆偏滞可笑。虽恒人皆得以知其妄也。而至于苏氏之学。反复抑扬。文饰假借。易惑而难辨。当斯道不明之日。操进退用舍之权。
其饰于外者。不足而然欤。抑其心有所偏系拗滞而然耶。由此观之。苏氏之学。亦可从而论之矣。今夫苏氏者。果何人哉。主老佛申韩之学。而文之以孔孟。挟纵横捭阖之术。而假之以仁义。高其眼。大其言。眩一世之耳目。苟非克察其心术之隐微。克究其学问之谬戾者。孰得以辨之哉。使此人得其位行其道。则其害人国家。可胜言哉。且夫今之罪王氏者。以其兴兵开衅。以伤国脉。而苏氏之初年。亦尝进用兵之说矣。今之罪王氏者。以其造法取利。以病生民。而苏氏之初年。亦尝进生财之说矣。及见王氏之为此事。遂致狼狈。乃一反前日用兵之说。以攻王氏兴兵之害。一反前日生财之说。以攻王氏取利之弊。此果其学贤于王氏而然欤。夫王氏之心。犹苏氏之心。苏氏之学。犹王氏之学也。心异其用。而不得其正则同。学异其致。而可以误国则同。然则荆公。特毕露手脚之子瞻也。子瞻即未试其术之荆公也。其得位也。乃王氏之不幸也。其不得位也。乃苏氏之幸也。然而王氏之学。如断鹌鹑之狱。制字说之书。皆偏滞可笑。虽恒人皆得以知其妄也。而至于苏氏之学。反复抑扬。文饰假借。易惑而难辨。当斯道不明之日。操进退用舍之权。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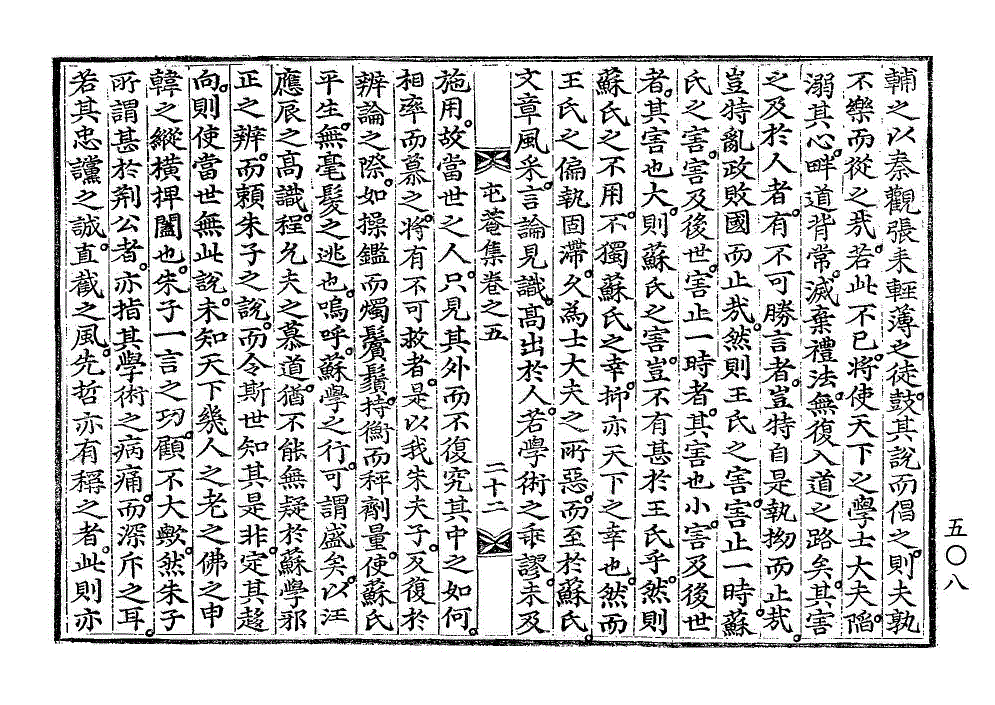 辅之以秦观张耒轻薄之徒。鼓其说而倡之。则夫孰不乐而从之哉。若此不已。将使天下之学士大夫。陷溺其心。畔道背常。灭弃礼法。无复入道之路矣。其害之及于人者。有不可胜言者。岂特自是执拗而止哉。岂特乱政败国而止哉。然则王氏之害。害止一时。苏氏之害。害及后世。害止一时者。其害也小。害及后世者。其害也大。则苏氏之害。岂不有甚于王氏乎。然则苏氏之不用。不独苏氏之幸。抑亦天下之幸也。然而王氏之偏执固滞。久为士大夫之所恶。而至于苏氏。文章风采。言论见识。高出于人。若学术之乖谬。未及施用。故当世之人。只见其外而不复究其中之如何。相率而慕之。将有不可救者。是以我朱夫子。反复于辨论之际。如操鉴而烛鬓须。持衡而秤剂量。使苏氏平生。无毫发之逃也。呜呼。苏学之行。可谓盛矣。以汪应辰之高识。程允夫之慕道。犹不能无疑于苏学邪正之辨。而赖朱子之说。而令斯世知其是非。定其趍向。则使当世无此说。未知天下几人之老之佛之申韩之纵横捭阖也。朱子一言之功。顾不大欤。然朱子所谓甚于荆公者。亦指其学术之病痛。而深斥之耳。若其忠谠之诚。直截之风。先哲亦有称之者。此则亦
辅之以秦观张耒轻薄之徒。鼓其说而倡之。则夫孰不乐而从之哉。若此不已。将使天下之学士大夫。陷溺其心。畔道背常。灭弃礼法。无复入道之路矣。其害之及于人者。有不可胜言者。岂特自是执拗而止哉。岂特乱政败国而止哉。然则王氏之害。害止一时。苏氏之害。害及后世。害止一时者。其害也小。害及后世者。其害也大。则苏氏之害。岂不有甚于王氏乎。然则苏氏之不用。不独苏氏之幸。抑亦天下之幸也。然而王氏之偏执固滞。久为士大夫之所恶。而至于苏氏。文章风采。言论见识。高出于人。若学术之乖谬。未及施用。故当世之人。只见其外而不复究其中之如何。相率而慕之。将有不可救者。是以我朱夫子。反复于辨论之际。如操鉴而烛鬓须。持衡而秤剂量。使苏氏平生。无毫发之逃也。呜呼。苏学之行。可谓盛矣。以汪应辰之高识。程允夫之慕道。犹不能无疑于苏学邪正之辨。而赖朱子之说。而令斯世知其是非。定其趍向。则使当世无此说。未知天下几人之老之佛之申韩之纵横捭阖也。朱子一言之功。顾不大欤。然朱子所谓甚于荆公者。亦指其学术之病痛。而深斥之耳。若其忠谠之诚。直截之风。先哲亦有称之者。此则亦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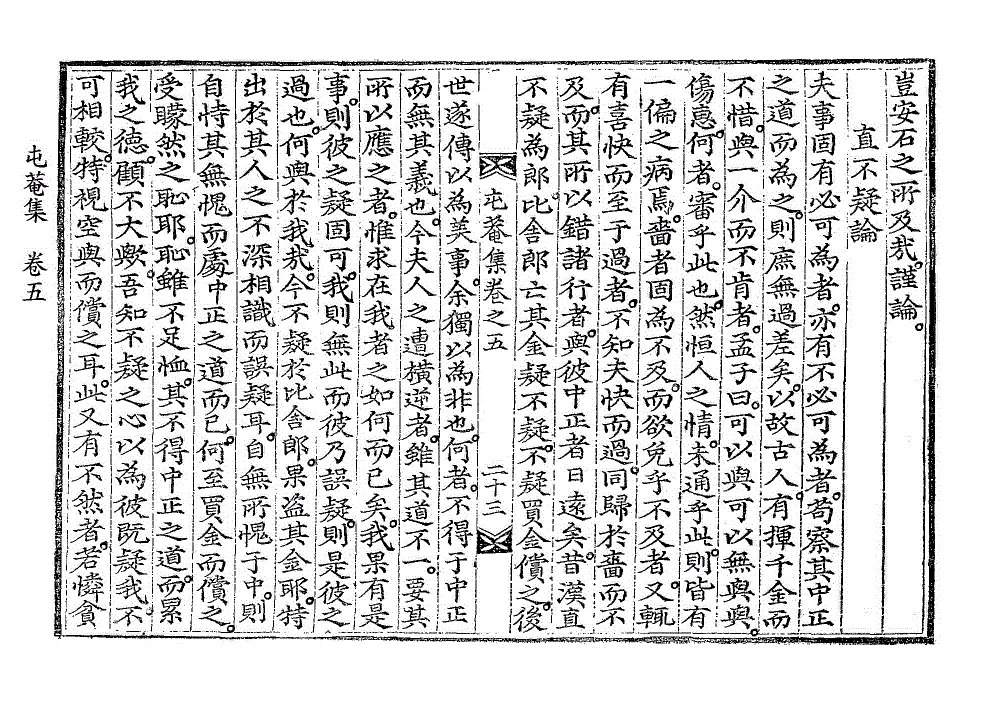 岂安石之所及哉。谨论。
岂安石之所及哉。谨论。直不疑论
夫事固有必可为者。亦有不必可为者。苟察其中正之道而为之。则庶无过差矣。以故古人。有挥千金而不惜。与一介而不肯者。孟子曰。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何者。审乎此也。然恒人之情。未通乎此。则皆有一偏之病焉。啬者固为不及。而欲免乎不及者。又辄有喜快而至于过者。不知夫快而过。同归于啬而不及。而其所以错诸行者。与彼中正者日远矣。昔汉直不疑为郎。比舍郎亡其金疑不疑。不疑买金偿之。后世遂传以为美事。余独以为非也。何者。不得于中正而无其义也。今夫人之遭横逆者。虽其道不一。要其所以应之者。惟求在我者之如何而已矣。我果有是事。则彼之疑固可。我则无此而彼乃误疑。则是彼之过也。何与于我哉。今不疑于比舍郎。果盗其金耶。特出于其人之不深相识而误疑耳。自无所愧于中。则自恃其无愧而处中正之道而已。何至买金而偿之。受矇然之耻耶。耻虽不足恤。其不得中正之道。而累我之德。顾不大欤。吾知不疑之心以为彼既疑我。不可相较。特视空与而偿之耳。此又有不然者。若怜贫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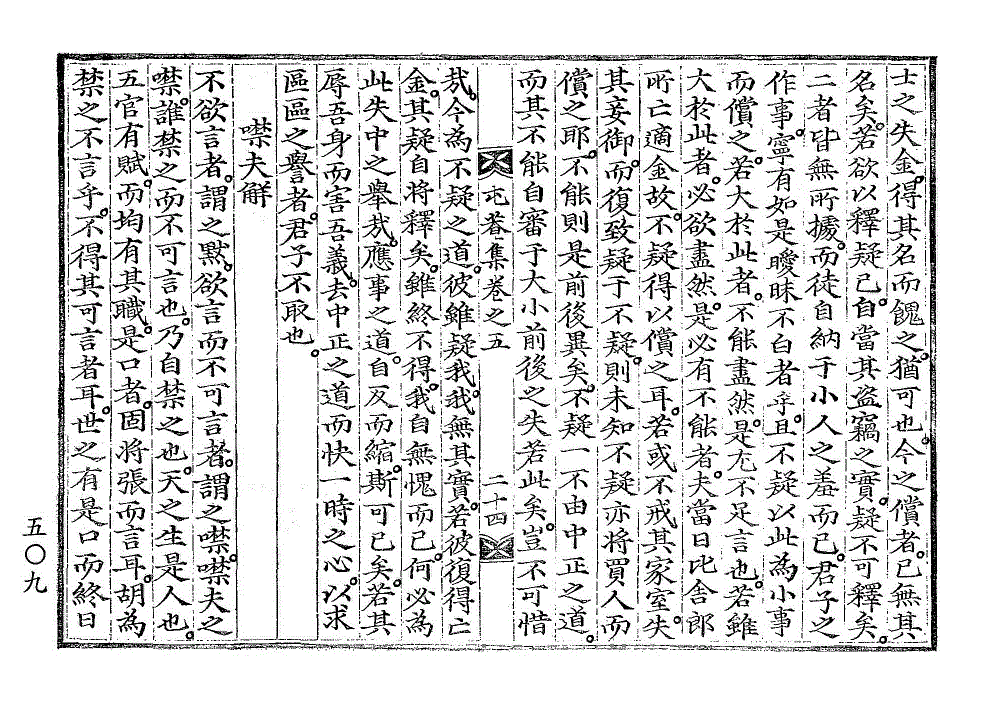 士之失金。得其名而馈之。犹可也。今之偿者。已无其名矣。若欲以释疑己。自当其盗窃之实。疑不可释矣。二者皆无所据。而徒自纳于小人之羞而已。君子之作事。宁有如是暧昧不白者乎。且不疑以此为小事而偿之。若大于此者。不能尽然。是尤不足言也。若虽大于此者。必欲尽然。是必有不能者。夫当日比舍郎所亡适金故。不疑得以偿之耳。若或不戒其家室。失其妾御。而复致疑于不疑。则未知不疑亦将买人而偿之耶。不能则是前后异矣。不疑一不由中正之道。而其不能自审于大小前后之失若此矣。岂不可惜哉。今为不疑之道。彼虽疑我。我无其实。若彼复得亡金。其疑自将释矣。虽终不得。我自无愧而已。何必为此失中之举哉。应事之道。自反而缩。斯可已矣。若其辱吾身而害吾义。去中正之道而快一时之心。以求区区之誉者。君子不取也。
士之失金。得其名而馈之。犹可也。今之偿者。已无其名矣。若欲以释疑己。自当其盗窃之实。疑不可释矣。二者皆无所据。而徒自纳于小人之羞而已。君子之作事。宁有如是暧昧不白者乎。且不疑以此为小事而偿之。若大于此者。不能尽然。是尤不足言也。若虽大于此者。必欲尽然。是必有不能者。夫当日比舍郎所亡适金故。不疑得以偿之耳。若或不戒其家室。失其妾御。而复致疑于不疑。则未知不疑亦将买人而偿之耶。不能则是前后异矣。不疑一不由中正之道。而其不能自审于大小前后之失若此矣。岂不可惜哉。今为不疑之道。彼虽疑我。我无其实。若彼复得亡金。其疑自将释矣。虽终不得。我自无愧而已。何必为此失中之举哉。应事之道。自反而缩。斯可已矣。若其辱吾身而害吾义。去中正之道而快一时之心。以求区区之誉者。君子不取也。噤夫解
不欲言者。谓之默。欲言而不可言者。谓之噤。噤夫之噤。谁禁之而不可言也。乃自禁之也。天之生是人也。五官有赋。而均有其职。是口者。固将张而言耳。胡为禁之不言乎。不得其可言者耳。世之有是口而终日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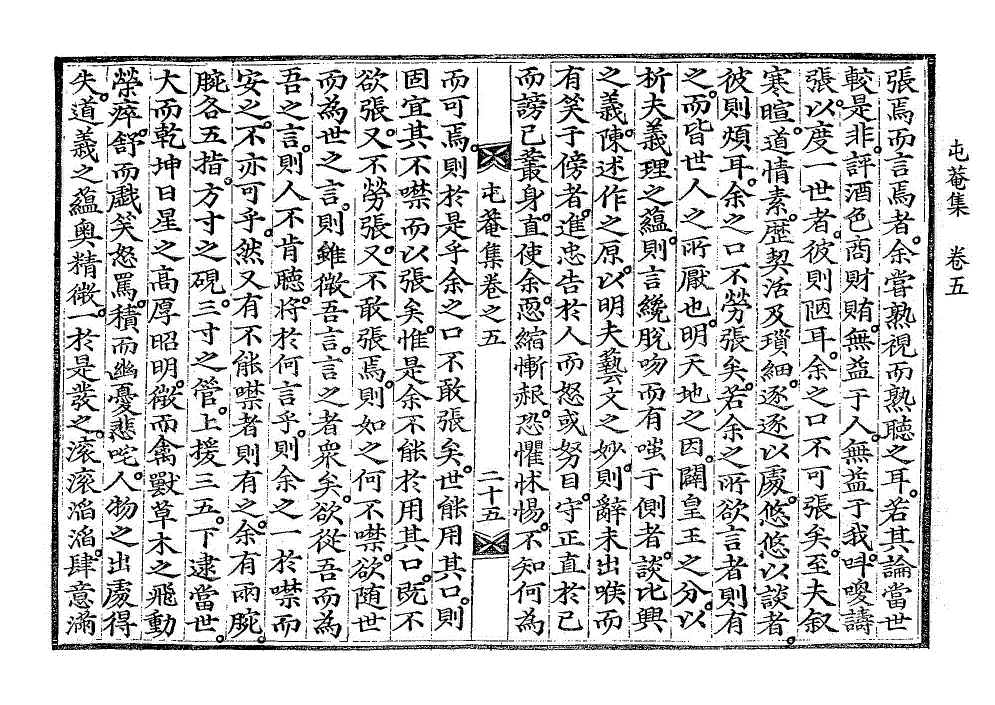 张焉而言焉者。余尝熟视而熟听之耳。若其论当世较是非。评酒色商财贿。无益于人。无益于我。叫唤诪张。以度一世者。彼则陋耳。余之口不可张矣。至夫叙寒暄。道情素。历契活及琐细。逐逐以处。悠悠以谈者。彼则烦耳。余之口不劳张矣。若余之所欲言者则有之。而皆世人之所厌也。明天地之因。辟皇王之分。以析夫义理之蕴。则言才脱吻而有嗤于侧者。谈比兴之义。陈述作之原。以明夫艺文之妙。则辞未出喉而有笑于傍者。进忠告于人而怒或努目。守正直于己而谤已丛身。直使余。恧缩惭赧。恐惧怵惕。不知何为而可焉。则于是乎余之口不敢张矣。世能用其口。则固宜其不噤而以张矣。惟是余不能于用其口。既不欲张。又不劳张。又不敢张焉。则如之何不噤。欲随世而为世之言。则虽微吾言。言之者众矣。欲从吾而为吾之言。则人不肯听。将于何言乎。则余之一于噤而安之。不亦可乎。然又有不能噤者则有之。余有两腕。腕各五指。方寸之砚。三寸之管。上援三五。下逮当世。大而乾坤日星之高厚昭明。微而禽兽草木之飞动荣瘁。舒而戏笑怒骂。积而幽忧悲咤。人物之出处得失。道义之蕴奥精微。一于是发之。滚滚滔滔。肆意满
张焉而言焉者。余尝熟视而熟听之耳。若其论当世较是非。评酒色商财贿。无益于人。无益于我。叫唤诪张。以度一世者。彼则陋耳。余之口不可张矣。至夫叙寒暄。道情素。历契活及琐细。逐逐以处。悠悠以谈者。彼则烦耳。余之口不劳张矣。若余之所欲言者则有之。而皆世人之所厌也。明天地之因。辟皇王之分。以析夫义理之蕴。则言才脱吻而有嗤于侧者。谈比兴之义。陈述作之原。以明夫艺文之妙。则辞未出喉而有笑于傍者。进忠告于人而怒或努目。守正直于己而谤已丛身。直使余。恧缩惭赧。恐惧怵惕。不知何为而可焉。则于是乎余之口不敢张矣。世能用其口。则固宜其不噤而以张矣。惟是余不能于用其口。既不欲张。又不劳张。又不敢张焉。则如之何不噤。欲随世而为世之言。则虽微吾言。言之者众矣。欲从吾而为吾之言。则人不肯听。将于何言乎。则余之一于噤而安之。不亦可乎。然又有不能噤者则有之。余有两腕。腕各五指。方寸之砚。三寸之管。上援三五。下逮当世。大而乾坤日星之高厚昭明。微而禽兽草木之飞动荣瘁。舒而戏笑怒骂。积而幽忧悲咤。人物之出处得失。道义之蕴奥精微。一于是发之。滚滚滔滔。肆意满屯庵集卷之五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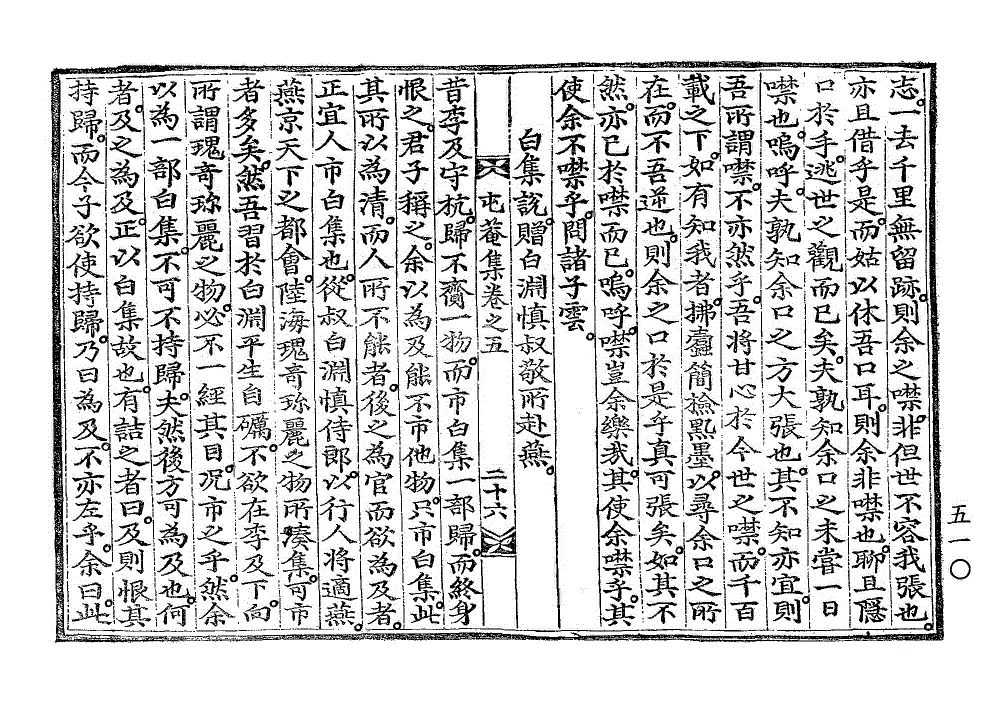 志。一去千里无留迹。则余之噤。非但世不容我张也。亦且借乎是。而姑以休吾口耳。则余非噤也。聊且隐口于手。逃世之观而已矣。夫孰知余口之未尝一日噤也。呜呼。夫孰知余口之方大张也。其不知亦宜。则吾所谓噤。不亦然乎。吾将甘心于今世之噤。而千百载之下。如有知我者。拂蠹简检䵝墨。以寻余口之所在。而不吾逆也。则余之口于是乎真可张矣。如其不然。亦已于噤而已。呜呼。噤岂余乐哉。其使余噤乎。其使余不噤乎。问诸子云。
志。一去千里无留迹。则余之噤。非但世不容我张也。亦且借乎是。而姑以休吾口耳。则余非噤也。聊且隐口于手。逃世之观而已矣。夫孰知余口之未尝一日噤也。呜呼。夫孰知余口之方大张也。其不知亦宜。则吾所谓噤。不亦然乎。吾将甘心于今世之噤。而千百载之下。如有知我者。拂蠹简检䵝墨。以寻余口之所在。而不吾逆也。则余之口于是乎真可张矣。如其不然。亦已于噤而已。呜呼。噤岂余乐哉。其使余噤乎。其使余不噤乎。问诸子云。白集说。赠白渊慎叔敬所赴燕。
昔李及守杭。归不赍一物。而市白集一部归。而终身恨之。君子称之。余以为及能不市他物。只市白集。此其所以为清。而人所不能者。后之为官而欲为及者。正宜人市白集也。从叔白渊慎侍郎。以行人将适燕。燕京天下之都会。陆海瑰奇珍丽之物所凑集。可市者多矣。然吾习于白渊平生自砺。不欲在李及下。向所谓瑰奇珍丽之物。必不一经其目。况市之乎。然余以为一部白集。不可不持归。夫然后方可为及也。何者。及之为及。正以白集故也。有诘之者曰。及则恨其持归。而今子欲使持归。乃曰为及。不亦左乎。余曰。此
屯庵集卷之五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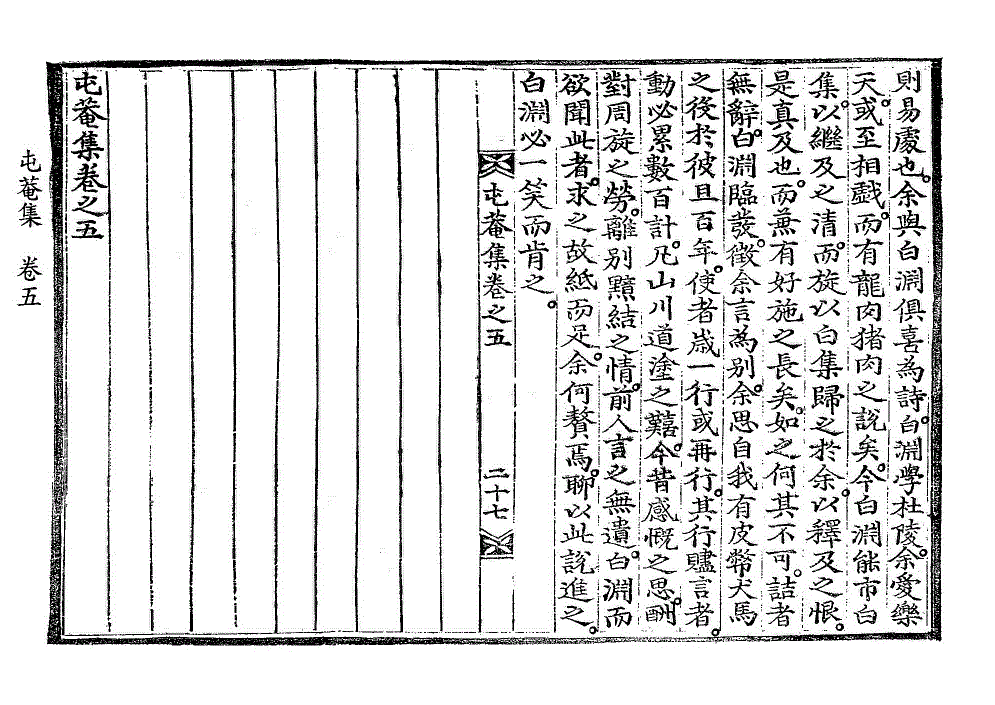 则易处也。余与白渊俱喜为诗。白渊学杜陵。余爱乐天。或至相戏。而有龙肉猪肉之说矣。今白渊能市白集。以继及之清。而旋以白集归之于余。以释及之恨。是真及也。而兼有好施之长矣。如之何其不可。诘者无辞。白渊临发。徵余言为别。余思自我有皮币犬马之役于彼且百年。使者岁一行或再行。其行赆言者。动必累数百计。凡山川道涂之艰。今昔感慨之思。酬对周旋之劳。离别黯结之情。前人言之无遗。白渊而欲闻此者。求之故纸而足。余何赘焉。聊以此说进之。白渊必一笑而肯之。
则易处也。余与白渊俱喜为诗。白渊学杜陵。余爱乐天。或至相戏。而有龙肉猪肉之说矣。今白渊能市白集。以继及之清。而旋以白集归之于余。以释及之恨。是真及也。而兼有好施之长矣。如之何其不可。诘者无辞。白渊临发。徵余言为别。余思自我有皮币犬马之役于彼且百年。使者岁一行或再行。其行赆言者。动必累数百计。凡山川道涂之艰。今昔感慨之思。酬对周旋之劳。离别黯结之情。前人言之无遗。白渊而欲闻此者。求之故纸而足。余何赘焉。聊以此说进之。白渊必一笑而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