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悔窝集卷四 第 x 页
悔窝集卷四
序
序
悔窝集卷四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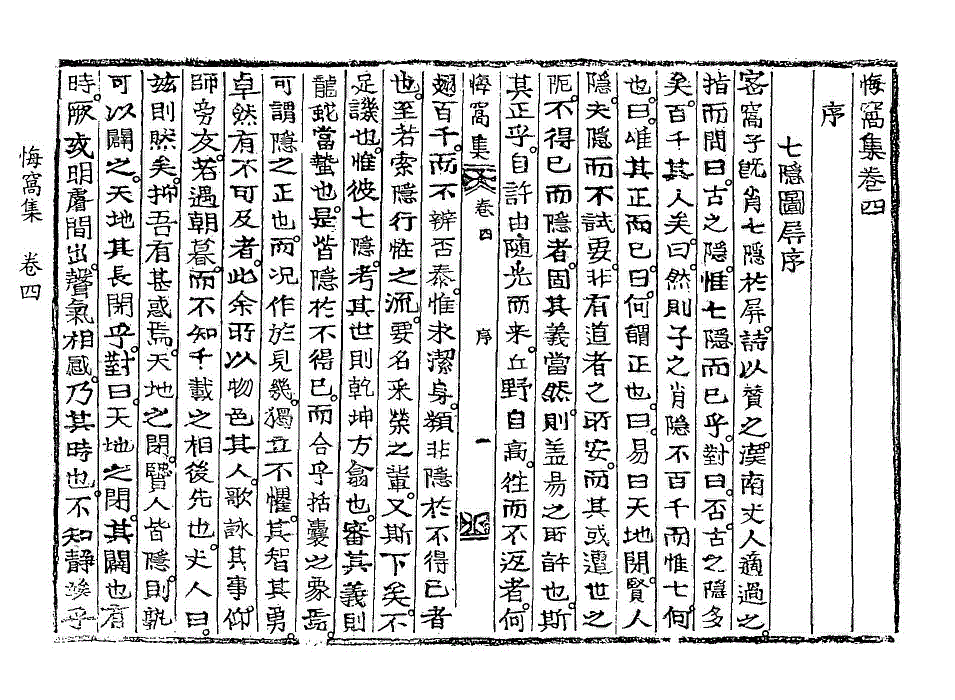 七隐图屏序
七隐图屏序密窝子既肖七隐于屏。诗以赞之。汉南丈人适过之。指而问曰。古之隐。惟七隐而已乎。对曰。否。古之隐多矣。百千其人矣。曰。然则子之肖隐不百千而惟七。何也。曰。唯其正而已。曰。何谓正也。曰。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夫隐而不试要。非有道者之所安。而其或遭世之阨。不得已而隐者。固其义当然。则盖易之所许也。斯其正乎。自许由,随,光而来。丘野自高。往而不返者。何翅百千。而不辨否泰。惟求洁身。类非隐于不得已者也。至若索隐行怪之流。要名采荣之辈。又斯下矣。不足讥也。惟彼七隐。考其世则乾坤方翕也。审其义则龙蛇当蛰也。是皆隐于不得已。而合乎括囊之象焉。可谓隐之正也。而况作于见几。独立不惧。其智其勇。卓然有不可及者。此余所以物色其人。歌咏其事。仰师旁友。若遇朝暮。而不知千载之相后先也。丈人曰。玆则然矣。抑吾有甚惑焉。天地之闭。贤人皆隐。则孰可以辟之。天地其长闭乎。对曰。天地之闭。其辟也有时。厥或明睿间出。声气相感。乃其时也。不知静俟乎
悔窝集卷四 第 3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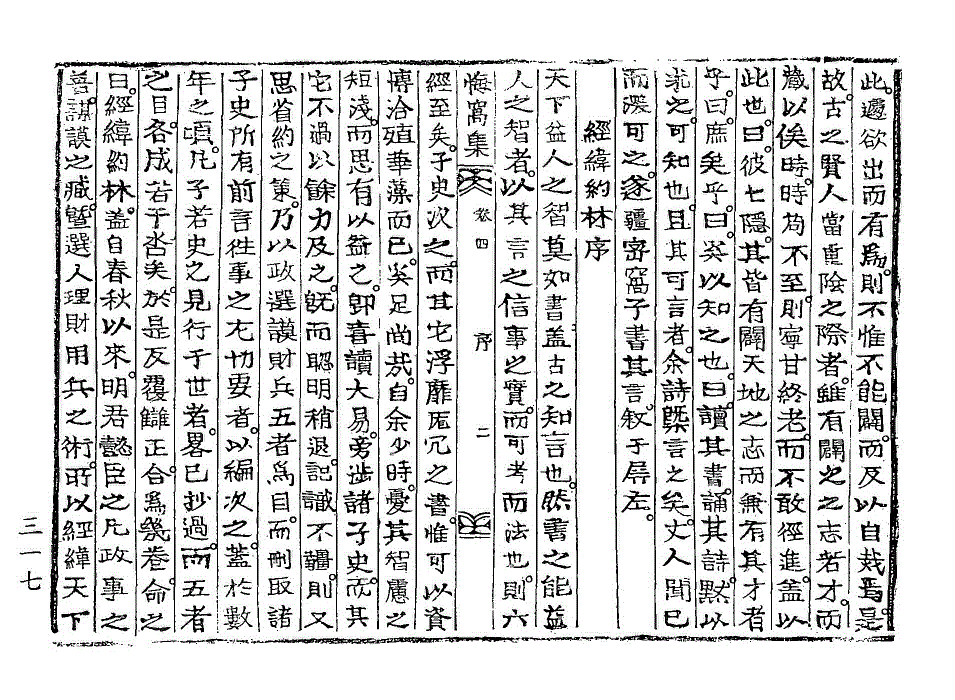 此。遽欲出而有为。则不惟不能辟。而反以自灾焉。是故。古之贤人当重阴之际者。虽有辟之之志若才。而藏以俟时。时苟不至。则宁甘终老。而不敢径进。盖以此也。曰。彼七隐。其皆有辟天地之志而兼有其才者乎。曰。庶矣乎。曰。奚以知之也。曰。读其书。诵其诗。默以求之。可知也。且其可言者。余诗槩言之矣。丈人闻已而深可之。遂疆密窝子书其言。叙于屏左。
此。遽欲出而有为。则不惟不能辟。而反以自灾焉。是故。古之贤人当重阴之际者。虽有辟之之志若才。而藏以俟时。时苟不至。则宁甘终老。而不敢径进。盖以此也。曰。彼七隐。其皆有辟天地之志而兼有其才者乎。曰。庶矣乎。曰。奚以知之也。曰。读其书。诵其诗。默以求之。可知也。且其可言者。余诗槩言之矣。丈人闻已而深可之。遂疆密窝子书其言。叙于屏左。经纬约林序
天下益人之智莫如书。盖古之知言也。然书之能益人之智者。以其言之信事之实。而可考而法也。则六经至矣。子史次之。而其它浮靡厖冗之书。惟可以资博洽殖华藻而已。奚足尚哉。自余少时。忧其智虑之短浅。而思有以益之。即喜读大易。旁涉诸子史。而其它不过以馀力及之。既而聪明稍退。记识不疆。则又思省约之策。乃以政选谟财兵五者为目。而删取诸子史所有前言往事之尤切要者。以编次之。盖于数年之顷。凡子若史之见行于世者。略已抄过。而五者之目。各成若干沓矣。于是反覆雠正。合为几卷。命之曰。经纬约林。盖自春秋以来。明君懿臣之凡政事之善。谋谟之臧。暨选人理财用兵之术。所以经纬天下
悔窝集卷四 第 318H 页
 而宜为后世法者。昭如列眉而居可考也。如天之福。使余果能会通于此。而卒收其效。则夙昔之忧。或庶乎瘳矣。幸孰大焉。是卷也。所选取者。专于子史。而不及于经者。经乃不刊之书。而不可去取之也。其目止于政选谟财兵。而不以礼乐继之者。急于先务也。亦冉氏俟君子之意也。嗟呼。天下之事。必天下人为之。而不在于彼。必在于己。然则凡天下之事。无大无小。己亦与有其责。而不可以不蚤讲也。然则余于是卷。与之始终。而蕲长其区区之智者。恶可已也。恶可已也。
而宜为后世法者。昭如列眉而居可考也。如天之福。使余果能会通于此。而卒收其效。则夙昔之忧。或庶乎瘳矣。幸孰大焉。是卷也。所选取者。专于子史。而不及于经者。经乃不刊之书。而不可去取之也。其目止于政选谟财兵。而不以礼乐继之者。急于先务也。亦冉氏俟君子之意也。嗟呼。天下之事。必天下人为之。而不在于彼。必在于己。然则凡天下之事。无大无小。己亦与有其责。而不可以不蚤讲也。然则余于是卷。与之始终。而蕲长其区区之智者。恶可已也。恶可已也。文宗序
所宗乎文者。纯乎道也。若文而诡道。道而厖。奚其宗。吾用此观之。天下之文。皆可知也。六经,四子。所以贯百世而通尊之者。道之体用。盖纯如也。自秦,汉来。用文名家者愈多。而揆之道则厖且诡矣。是以知者则替之。大道散。文亦日敝。历千有馀年。入于宋。若周,程,张,朱诸老先生前后作。然后实凝斯道而完之。其所著文章。始可与经若子。为之羽翼。而顾其最可宗者。亦各有一二篇焉。濂溪之太极图说。横渠之西铭。明道之十事封事。伊川之易,春秋传序。考亭之中庸序
悔窝集卷四 第 318L 页
 戊申封事是已。然说及铭及三序。所以明天下之理也。道之体也。其两封事则所以成天下之务也。道之用也。体用则该而道斯纯矣。抑汉之诸葛武侯出师前表。唐之韩文公论佛骨表。刘去华太和对策。宋之胡邦衡请斩三人疏。盖以明兴复之大义。斥空寂之夷法。辨篡弑之阴祸。折媾和之邪议。要使天统尊。正教敦。主威专。彝伦章。而使夫僭伪,凶忍,诞妄,奸欺之徒。有所惧而不得肆。则虽于道所涉者浅。而各有以得其用之分数。视诸家之厖且诡于道者。殆异日道也。可无敬乎。余小子窃不自揣。敢以道之体用。分五先生七篇之文。汇为上下二编。又取武侯表以下四篇。附之后。别为一编。合写于一卷。题之曰文宗。以拟次经子而读诵焉。呜呼。天下之文。六经则纯。四子配之。而傍选历古可以继之者。惟此卷尽之。若是乎为文之难也。有志于道者。不宗乎此。复何宗哉。
戊申封事是已。然说及铭及三序。所以明天下之理也。道之体也。其两封事则所以成天下之务也。道之用也。体用则该而道斯纯矣。抑汉之诸葛武侯出师前表。唐之韩文公论佛骨表。刘去华太和对策。宋之胡邦衡请斩三人疏。盖以明兴复之大义。斥空寂之夷法。辨篡弑之阴祸。折媾和之邪议。要使天统尊。正教敦。主威专。彝伦章。而使夫僭伪,凶忍,诞妄,奸欺之徒。有所惧而不得肆。则虽于道所涉者浅。而各有以得其用之分数。视诸家之厖且诡于道者。殆异日道也。可无敬乎。余小子窃不自揣。敢以道之体用。分五先生七篇之文。汇为上下二编。又取武侯表以下四篇。附之后。别为一编。合写于一卷。题之曰文宗。以拟次经子而读诵焉。呜呼。天下之文。六经则纯。四子配之。而傍选历古可以继之者。惟此卷尽之。若是乎为文之难也。有志于道者。不宗乎此。复何宗哉。禹准卿续古风序
昔予朱子。盖取陈伯玉感遇之作。而病其指往往杂出于仙灵佛幻之绪馀。殆如金膏水碧诸奇怪物之若可宝玩。而不适于常用。则遂以道之贯乎天人。亘乎古今。而日可见之之实。次第为诗。命之曰感兴。诒
悔窝集卷四 第 319H 页
 之后学。以开其蒙。是盖拟古作者之体。而实以发吾之蕴也。梅阿隐者。禹君准卿。好学士也。与其兄孤山公。早悦考亭氏之道。求之遗编。正于有道。备知自治治人之术。及其既壮。始欲出而有为。则顾厄于时。无所试其学。于是乎其综古覈今之识。忧时慨俗之怀。积郁于中。而不能终闭。则思欲一形于歌咏之发。而所谓李供奉五十九首之什。适有以触其机。遂乃仍其题按其韵。续以和之。必尽其数而肯已。其意固已悲矣。然白以迈往之气。矜其超轶之才。自以蹈晋跨魏。凌驾秦汉。能复其一死不还之周雅。而徐考其兴寄之极于高远者。则亦不过祖伯玉之为。而猖狂自恣。将又甚焉。恶可与熙熙曲直之体。同一日道也。是以准卿又未始不病乎此。至其续之也。纲纪以挈之。平实以畅之。其名则续。其义则反。岂所谓借古发之善于自道者耶。夫白固子昂之流。亚准卿之学。实慕考亭氏而不怠。然则准卿之为此。所以效感兴之拟于感遇者盖无疑。而凡为州党之子弟者。幸得以诵之。则其启发之益。可胜既乎。抑其词。宁拙而不敢奇。宁腐而不敢新。视白之清新隽逸。不翅逡巡。则宜若可厌。然感遇感兴。其为词新腐奇拙。无亦有间乎。盖
之后学。以开其蒙。是盖拟古作者之体。而实以发吾之蕴也。梅阿隐者。禹君准卿。好学士也。与其兄孤山公。早悦考亭氏之道。求之遗编。正于有道。备知自治治人之术。及其既壮。始欲出而有为。则顾厄于时。无所试其学。于是乎其综古覈今之识。忧时慨俗之怀。积郁于中。而不能终闭。则思欲一形于歌咏之发。而所谓李供奉五十九首之什。适有以触其机。遂乃仍其题按其韵。续以和之。必尽其数而肯已。其意固已悲矣。然白以迈往之气。矜其超轶之才。自以蹈晋跨魏。凌驾秦汉。能复其一死不还之周雅。而徐考其兴寄之极于高远者。则亦不过祖伯玉之为。而猖狂自恣。将又甚焉。恶可与熙熙曲直之体。同一日道也。是以准卿又未始不病乎此。至其续之也。纲纪以挈之。平实以畅之。其名则续。其义则反。岂所谓借古发之善于自道者耶。夫白固子昂之流。亚准卿之学。实慕考亭氏而不怠。然则准卿之为此。所以效感兴之拟于感遇者盖无疑。而凡为州党之子弟者。幸得以诵之。则其启发之益。可胜既乎。抑其词。宁拙而不敢奇。宁腐而不敢新。视白之清新隽逸。不翅逡巡。则宜若可厌。然感遇感兴。其为词新腐奇拙。无亦有间乎。盖悔窝集卷四 第 319L 页
 专于实者。文固不暇为。观于布帛菽粟之实。可知之矣。虽然。粟布之与金膏水碧。世有能辨其贵者否。呜呼欷矣。
专于实者。文固不暇为。观于布帛菽粟之实。可知之矣。虽然。粟布之与金膏水碧。世有能辨其贵者否。呜呼欷矣。叙闵士卫屏子
屏之图。盖司马文正公之洛上独乐园也。吾友闵士卫。官桂坊而得之以示余。其图出于庸史之意。造未必称其本境。然要亦有彷佛者。为之叙曰。古之君子。能独乐于身。然后有以能及人。与天下同其乐焉。盖君子之所独乐者。道也。其所同乐者。道之推也。夫平居燕处。读皇王诗书典礼之说。观天人性命要眇之原。精粗显微。独觉其然。而反以实之于己。遂使此道为我之有。则于是吾之心。快然有以自足。无所假于外物。而其为乐有不可胜穷者矣。君子之所谓能独乐者然也。而及其出而有为于世。则不过推其素所乐于天下。使天下无一物之不与获焉。如古之天民伊尹太公之流者。固皆能乎此也。文正公在宋熙宁中。尝厄于时。退而家于洛。治数亩之园。植以花木。为一室。读书其中。凡其潜玩实践之勤。暨夫游神养性。与道徘徊之适。据公之自为记可见矣。公所性纯粹。重以静修之功如此。宜其学之克造乎诚一。而俯仰
悔窝集卷四 第 320H 页
 上下。无所愧怍者矣。然则公之居此也。能独出于万物之表。而其中盎然乐之。终身不厌者。无亦近于伊尹之处莘野。太公之在渭滨。而其所以命之名者。真可谓识其实者也。虽然。公则能乐矣。天下之疾痛愁劳者。相与环向而求乐于公。公虽欲已之。其可忍乎。故公为天下复起而当元祐之初。则其为政一出于至诚。苟利于民。罢行不疑。果能大慰烝庶之望。而使之各得其所欲。向使假之年。殆将凛凛于三代之复还。而与夫人偕之乎太康之域矣。此岂非平日所独乐者之推也耶。呜呼盛哉。孟子称古人之嚣嚣自乐者。而曰穷则能独善其身。达则能兼善天下。非伊吕之比于道者。不足以当此而下之。则惟公庶几其人也。然则是园也。其可使莘野渭滨专美于古。而独不足参之而为三者耶。呜呼。其可模也已。
上下。无所愧怍者矣。然则公之居此也。能独出于万物之表。而其中盎然乐之。终身不厌者。无亦近于伊尹之处莘野。太公之在渭滨。而其所以命之名者。真可谓识其实者也。虽然。公则能乐矣。天下之疾痛愁劳者。相与环向而求乐于公。公虽欲已之。其可忍乎。故公为天下复起而当元祐之初。则其为政一出于至诚。苟利于民。罢行不疑。果能大慰烝庶之望。而使之各得其所欲。向使假之年。殆将凛凛于三代之复还。而与夫人偕之乎太康之域矣。此岂非平日所独乐者之推也耶。呜呼盛哉。孟子称古人之嚣嚣自乐者。而曰穷则能独善其身。达则能兼善天下。非伊吕之比于道者。不足以当此而下之。则惟公庶几其人也。然则是园也。其可使莘野渭滨专美于古。而独不足参之而为三者耶。呜呼。其可模也已。孙子十三篇去注序
儒者不言兵。兵非儒者之所急。然儒必极天下之务。而耻一二之不通。则独于兵遗之哉。吾夫子在卫曰。俎豆之事。尝学之。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此为灵公好武而言可矣。若夫子行三军。则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尝曰。我战则克。相夹谷之会。则实以兵从。
悔窝集卷四 第 320L 页
 遂抑齐人之祸心。而使不得逞。冉有胜敌。或问能战之故。则曰求尝学于夫子矣。盖夫子固尝志于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然其明于兵如此。抑衰世不得已之意也。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则其谁能去兵而世运日下。金革之事。无时而息。使为士者。惟知切切于性命之察。文为之肄。而不复以馀力及于兵。则不几于拘学之归而卒为圣徒所笑也乎。余为是惧。尝于经史之暇。辄思疆其不能。则既博涉古之兵流。而考其臧否矣。凡古之兵书。若汉淮阴侯之所申明者。已多不见于世。世之所尚。唯六韬三略等七书。号为武经者为最盛。然韬略虽谓太公之所作。而其言鄙诈。要非佐王之道。如司马,尉缭,吴子三家。间亦多伪。未必一出于其人。而李卫公则直阮逸之假为也。独所谓孙武十三篇者。余盖反复参伍。观其为术独至。脩辞古奇。决知其自武出而有不可诬者矣。夫武特战国之雄。而其论兵之要。不过曰诡道而已。则是固仁义之所羞而制节之所讳也。然其书究后世用兵变化之极。有以明其术而不复为赝说所乱。故古之知兵者。固皆宗知。孙膑,韩信,赵充国,诸葛武侯诸子之所称引古兵法者。槩皆出于此。而至于曹孟德。则从以
遂抑齐人之祸心。而使不得逞。冉有胜敌。或问能战之故。则曰求尝学于夫子矣。盖夫子固尝志于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然其明于兵如此。抑衰世不得已之意也。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则其谁能去兵而世运日下。金革之事。无时而息。使为士者。惟知切切于性命之察。文为之肄。而不复以馀力及于兵。则不几于拘学之归而卒为圣徒所笑也乎。余为是惧。尝于经史之暇。辄思疆其不能。则既博涉古之兵流。而考其臧否矣。凡古之兵书。若汉淮阴侯之所申明者。已多不见于世。世之所尚。唯六韬三略等七书。号为武经者为最盛。然韬略虽谓太公之所作。而其言鄙诈。要非佐王之道。如司马,尉缭,吴子三家。间亦多伪。未必一出于其人。而李卫公则直阮逸之假为也。独所谓孙武十三篇者。余盖反复参伍。观其为术独至。脩辞古奇。决知其自武出而有不可诬者矣。夫武特战国之雄。而其论兵之要。不过曰诡道而已。则是固仁义之所羞而制节之所讳也。然其书究后世用兵变化之极。有以明其术而不复为赝说所乱。故古之知兵者。固皆宗知。孙膑,韩信,赵充国,诸葛武侯诸子之所称引古兵法者。槩皆出于此。而至于曹孟德。则从以悔窝集卷四 第 3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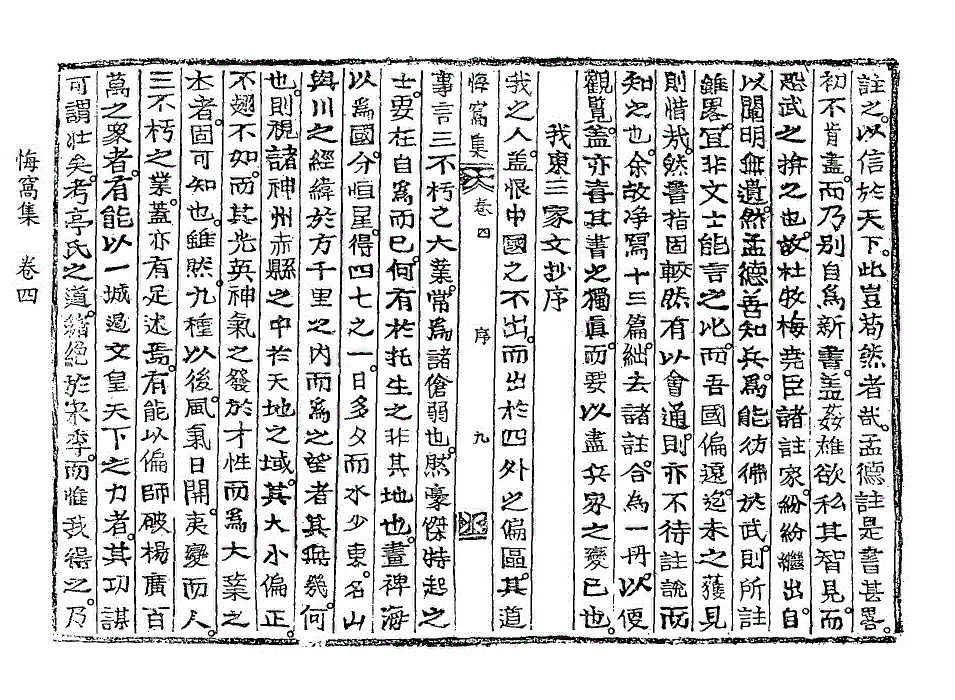 注之。以信于天下。此岂苟然者哉。孟德注是书甚略。初不肯尽。而乃别自为新书。盖奸雄欲私其智见。而恐武之掩之也。故杜牧,梅尧臣诸注家。纷纷继出。自以阐明无遗。然孟德善知兵。为能彷佛于武。则所注虽略。宜非文士能言之比。而吾国偏远。迄未之获见则惜哉。然书指固较然有以会通。则亦不待注说而知之也。余故净写十三篇。绌去诸注。合为一册。以便观览。盖亦喜其书之独真。而要以尽兵家之变已也。
注之。以信于天下。此岂苟然者哉。孟德注是书甚略。初不肯尽。而乃别自为新书。盖奸雄欲私其智见。而恐武之掩之也。故杜牧,梅尧臣诸注家。纷纷继出。自以阐明无遗。然孟德善知兵。为能彷佛于武。则所注虽略。宜非文士能言之比。而吾国偏远。迄未之获见则惜哉。然书指固较然有以会通。则亦不待注说而知之也。余故净写十三篇。绌去诸注。合为一册。以便观览。盖亦喜其书之独真。而要以尽兵家之变已也。我东三家文抄序
我之人。盖恨中国之不出。而出于四外之偏区。其道事言三不朽之大业。常为诸伧弱也。然豪杰特起之士。要在自为而已。何有于托生之非其地也。画裨海以为国。分恒星。得四七之一。日多夕而水少东。名山与川之经纬于方千里之内而为之望者其无几。何也。则视诸神州赤县之中于天地之域。其大小偏正。不翅不如。而其光英神气之发于才性而为大业之本者。固可知也。虽然。九种以后。风气日开。夷变而人。三不朽之业。盖亦有足述焉。有能以偏师破杨广百万之众者。有能以一城遏文皇天下之力者。其功谋可谓壮矣。考亭氏之道。绪绝于宋季。而惟我得之。乃
悔窝集卷四 第 321L 页
 本朝一二前修其全体大用之学。殆非黄,真,许,薛所能抏也。则问学之懿。又何如也。至于文章之作。最初崔孤云。固为称首。而其遗文不少传。若牧隐之独擅于丽。若简易,溪谷之代兴于 本朝。则实数千百年来之选也。牧隐之文。气机浑然。殆于神化。简易辞尚悍洁。而溪谷理主雅驯。其于典则。皆森如也。以当时中国之作家。方之原功景濂。仅与牧老可伯仲。而王弇州钱虞山诸公。未必不逡巡于简与溪焉尔。噫。斯其业。虽若下于向之二者。然均之豪杰之士。秉其独至之见。卓然有以自为。而未始知生地之有偏正。赋气之有旺微也。不已多乎。肆余约取三家文各数十首。合写为一卷。附此言于其端。以见先辈述作之盛如此。可与夫摧隋却唐之功。绍明程朱之学。皆足以不朽于来世。而虽使方行于天下。无复强对之可畏也。则庶吾党之慨然有志者。尚可以知进取之在我。而不复以托生之非地为深恨也夫。
本朝一二前修其全体大用之学。殆非黄,真,许,薛所能抏也。则问学之懿。又何如也。至于文章之作。最初崔孤云。固为称首。而其遗文不少传。若牧隐之独擅于丽。若简易,溪谷之代兴于 本朝。则实数千百年来之选也。牧隐之文。气机浑然。殆于神化。简易辞尚悍洁。而溪谷理主雅驯。其于典则。皆森如也。以当时中国之作家。方之原功景濂。仅与牧老可伯仲。而王弇州钱虞山诸公。未必不逡巡于简与溪焉尔。噫。斯其业。虽若下于向之二者。然均之豪杰之士。秉其独至之见。卓然有以自为。而未始知生地之有偏正。赋气之有旺微也。不已多乎。肆余约取三家文各数十首。合写为一卷。附此言于其端。以见先辈述作之盛如此。可与夫摧隋却唐之功。绍明程朱之学。皆足以不朽于来世。而虽使方行于天下。无复强对之可畏也。则庶吾党之慨然有志者。尚可以知进取之在我。而不复以托生之非地为深恨也夫。东避录序
古之人于丧乱漂流之际。皆有所叙述。以识其身心之所困迫。时变之所极挚。若周人之赋兔爰。杜甫之作北征。李忠定之撰传信录之类是已。此岂惟自道
悔窝集卷四 第 322H 页
 其不幸而已。抑以写夫忧君与国。感愤悲恫之不能已者。盖亦忠臣孝子之志也欤。余以丁未秋。去官乡居。及是年季春之末。违清州狂寇之难。挈家属。过江逾月阿岭。侨处于堤之陶村。于时莽戎卒兴。远近震骇。士女之奔迸于道涂者。若兽挺而禽窜。余窭人也。家不畜仆马。只与儿曹步走。日中行五十里之远。足伤脚疼。饥渴交逼。小儿至有啼泣者。况囊袋之粟。不能支数日。日采山溪之毛。和糠覈以充朝晡。其险艰之备尝。可知也。适有天力。小丑旋剿。而顾世家名族之蔓延作逆者。殆为参国之二。外乱虽戢。内虞方殷。重以民穷财匮。势迫于土崩。是则周嫠靡暇于恤纬。雅人不遑于假寐者矣。尝读兔爰,北征之诗及传信录等。窃悲其人忠孝之盛。而或疑其过于忧伤。以余之遭今日者方之。殆亦有甚焉。盖悬想与躬见。不翅不如也。乃于潜藏畏约之境。吞声抆血之馀。辄取纸笔。略识避寇以来日间诸杂事。与夫往来诸言之及于讨贼者。用月日编次之。始自三月十九日己巳。讫于四月庚戌之晦。题之曰东避录。又集所作近体五七言若干篇附于后。嗟夫。试以此录。参之于周唐宋三子者之述作。则虽人有贤愚之分。事有大小之异。
其不幸而已。抑以写夫忧君与国。感愤悲恫之不能已者。盖亦忠臣孝子之志也欤。余以丁未秋。去官乡居。及是年季春之末。违清州狂寇之难。挈家属。过江逾月阿岭。侨处于堤之陶村。于时莽戎卒兴。远近震骇。士女之奔迸于道涂者。若兽挺而禽窜。余窭人也。家不畜仆马。只与儿曹步走。日中行五十里之远。足伤脚疼。饥渴交逼。小儿至有啼泣者。况囊袋之粟。不能支数日。日采山溪之毛。和糠覈以充朝晡。其险艰之备尝。可知也。适有天力。小丑旋剿。而顾世家名族之蔓延作逆者。殆为参国之二。外乱虽戢。内虞方殷。重以民穷财匮。势迫于土崩。是则周嫠靡暇于恤纬。雅人不遑于假寐者矣。尝读兔爰,北征之诗及传信录等。窃悲其人忠孝之盛。而或疑其过于忧伤。以余之遭今日者方之。殆亦有甚焉。盖悬想与躬见。不翅不如也。乃于潜藏畏约之境。吞声抆血之馀。辄取纸笔。略识避寇以来日间诸杂事。与夫往来诸言之及于讨贼者。用月日编次之。始自三月十九日己巳。讫于四月庚戌之晦。题之曰东避录。又集所作近体五七言若干篇附于后。嗟夫。试以此录。参之于周唐宋三子者之述作。则虽人有贤愚之分。事有大小之异。悔窝集卷四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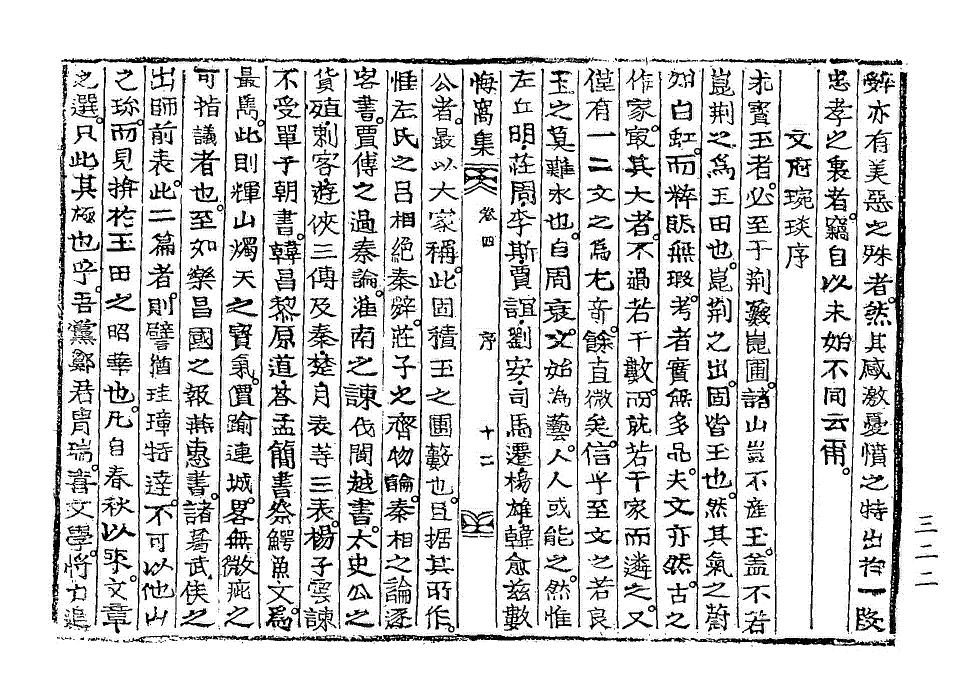 辞亦有美恶之殊者。然其感激忧愤之特出于一段忠孝之衷者。窃自以未始不同云尔。
辞亦有美恶之殊者。然其感激忧愤之特出于一段忠孝之衷者。窃自以未始不同云尔。文府琬琰序
求宝玉者。必至于荆薮昆圃。诸山岂不产玉。盖不若昆荆之为玉田也。昆荆之出。固皆玉也。然其气之蔚如白虹。而粹然无瑕。考者实无多品。夫文亦然。古之作家。最其大者。不过若干数。而就若干家而遴之。又仅有一二文之为尤奇。馀直微矣。信乎至文之若良玉之莫难求也。自周衰。文始为艺。人人或能之。然惟左丘明,庄周,李斯,贾谊,刘安,司马迁,杨雄,韩愈玆数公者。最以大家称。此固积玉之圃薮也。且据其所作。惟左氏之吕相绝秦辞。庄子之齐物论。秦相之论逐客书。贾傅之过秦论。淮南之谏伐闽越书。太史公之货殖,刺客,游侠三传及秦,楚,月表等三表。杨子云谏不受单于朝书。韩昌黎原道,答孟简书,祭鳄鱼文。为最隽。此则辉山烛天之宝气。价踰连城。略无微疵之可指议者也。至如乐昌国之报燕惠书。诸葛武侯之出师前表。此二篇者。则譬犹圭璋特达。不可以他山之珍。而见掩于玉田之昭华也。凡自春秋以来。文章之选。只此其极也乎。吾党郑君胄瑞。喜文学。将力追
悔窝集卷四 第 323H 页
 古作者为徒。而疑于璞鼠之辨。间尝谂于余。余嘉其意。遂为列之如此。君即谋于其同志者朴秀才道显。合写为一册。题之曰文府琬琰。以为拟议准则之资。其可谓信之至而好之笃也。夫以终古为文之盛。而择其如玉之粹然致美者。若此其甚少。是知文章之难为。殆非学力之所可及也。然试稽古人于此。未始不毕其才力而为之也。今诸君之学之也。亦当审吾才力之能毕与不能毕而已矣。夫玉质之一定者也。文艺之多变者也。质之一定者。瑕瑜难移。艺之多变者。纯驳可化。是则文与玉。品同而理殊。亦诸君所宜知也。勉之哉勉之哉。
古作者为徒。而疑于璞鼠之辨。间尝谂于余。余嘉其意。遂为列之如此。君即谋于其同志者朴秀才道显。合写为一册。题之曰文府琬琰。以为拟议准则之资。其可谓信之至而好之笃也。夫以终古为文之盛。而择其如玉之粹然致美者。若此其甚少。是知文章之难为。殆非学力之所可及也。然试稽古人于此。未始不毕其才力而为之也。今诸君之学之也。亦当审吾才力之能毕与不能毕而已矣。夫玉质之一定者也。文艺之多变者也。质之一定者。瑕瑜难移。艺之多变者。纯驳可化。是则文与玉。品同而理殊。亦诸君所宜知也。勉之哉勉之哉。古文字汇序
夫古之人文。经纬天地。实与日星云汉之华。河岳金璞之英。交敷互宣。错成其章。所谓人文者。礼乐制度文章字书之属。是也。此皆元古圣神。以其首出之智。因天地自然之法象。而刱为之用。垂百代不刊之典则。岂后世思虑之精。手目之巧所能及哉。世日下。道亦日苟。人各矜其小慧。竞为便利之图。则如古礼乐之物。皆已侵蚀无馀。而至于字体书势。亦日月浸化。分隶行草。纷然以出。则轩颉之遗法。几乎泯矣。是则
悔窝集卷四 第 3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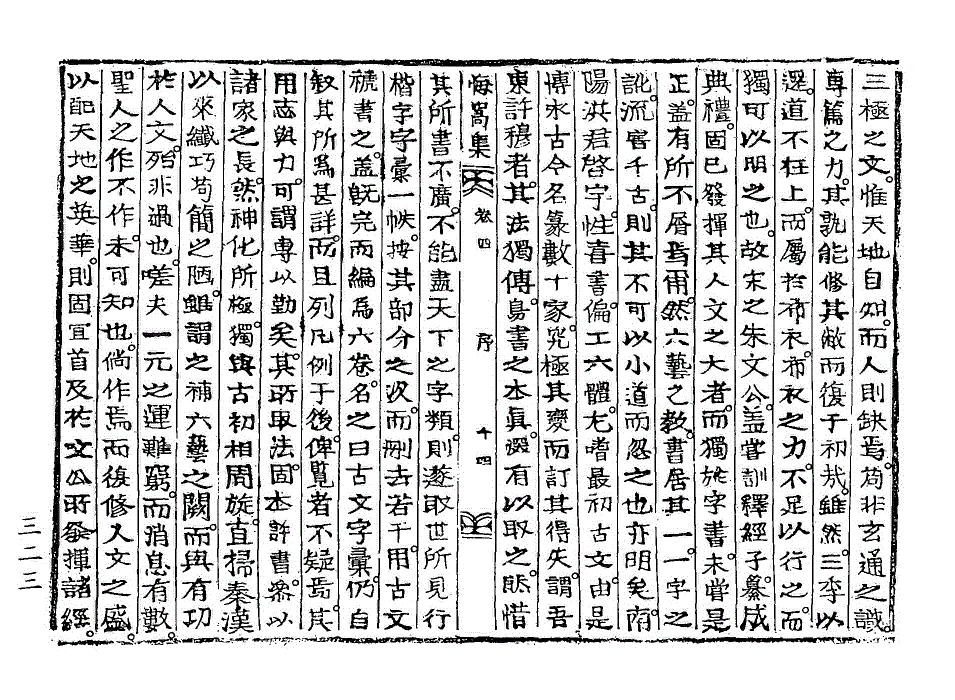 三极之文。惟天地自如。而人则缺焉。苟非玄通之识。专笃之力。其孰能修其敝而复于初哉。虽然。三季以还。道不在上。而属于布衣。布衣之力。不足以行之。而独可以明之也。故宋之朱文公。盖尝训释经子。纂成典礼。固已发挥其人文之大者。而独于字书。未尝是正。盖有所不屑焉尔。然六艺之教。书居其一。一字之讹。流害千古。则其不可以小道而忽之也亦明矣。南阳洪君启宇。性喜书。偏工六体。尤嗜最初古文。由是博求古今名篆数十家。究极其变而订其得失。谓吾东许穆者。其法独传。鸟书之本真。深有以取之。然惜其所书不广。不能尽天下之字类。则遂取世所见行楷字字汇一帙。按其部分之次。而删去若干。用古文褫书之。盖既完而编为六卷。名之曰古文字汇。仍自叙其所为甚详。而且列凡例于后。俾览者不疑焉。其用志与力。可谓专以勤矣。其所取法。固本许书。参以诸家之长。然神化所极。独与古初相周旋。直扫秦,汉以来纤巧苟简之陋。虽谓之补六艺之阙。而与有功于人文。殆非过也。嗟夫一元之运难穷。而消息有数。圣人之作不作。未可知也。倘作焉而复修人文之盛。以配天地之英华。则固宜首及于文公所发挥诸经。
三极之文。惟天地自如。而人则缺焉。苟非玄通之识。专笃之力。其孰能修其敝而复于初哉。虽然。三季以还。道不在上。而属于布衣。布衣之力。不足以行之。而独可以明之也。故宋之朱文公。盖尝训释经子。纂成典礼。固已发挥其人文之大者。而独于字书。未尝是正。盖有所不屑焉尔。然六艺之教。书居其一。一字之讹。流害千古。则其不可以小道而忽之也亦明矣。南阳洪君启宇。性喜书。偏工六体。尤嗜最初古文。由是博求古今名篆数十家。究极其变而订其得失。谓吾东许穆者。其法独传。鸟书之本真。深有以取之。然惜其所书不广。不能尽天下之字类。则遂取世所见行楷字字汇一帙。按其部分之次。而删去若干。用古文褫书之。盖既完而编为六卷。名之曰古文字汇。仍自叙其所为甚详。而且列凡例于后。俾览者不疑焉。其用志与力。可谓专以勤矣。其所取法。固本许书。参以诸家之长。然神化所极。独与古初相周旋。直扫秦,汉以来纤巧苟简之陋。虽谓之补六艺之阙。而与有功于人文。殆非过也。嗟夫一元之运难穷。而消息有数。圣人之作不作。未可知也。倘作焉而复修人文之盛。以配天地之英华。则固宜首及于文公所发挥诸经。悔窝集卷四 第 324H 页
 举以措之无遗。而若洪君六卷之书。亦得以见采。必不以地遐物微而废之也。不亦盛乎。今姑刻之贞石。藏于名山。以待其时可矣。洪君其珍之哉。珍之哉。
举以措之无遗。而若洪君六卷之书。亦得以见采。必不以地遐物微而废之也。不亦盛乎。今姑刻之贞石。藏于名山。以待其时可矣。洪君其珍之哉。珍之哉。遁叟诗集序
夫士用百年之涯。而毕其力于艺学。既不能当世施为。而且使湮灭于无闻。则讵不终古而有馀恨者欤。故董生赋士。不遇以自泄其不幸。而杨子云不能不俟乎子云之复出。其所感之深。皆可知也。吾宗遁叟公名守基。当 穆庙时。以行义荐于 朝。为教官旋罢。老卒于家。其文词郁然名于世。殆可与并时诸钜公。上下驰骋。以焕 王猷贲治道无不及。然特困于所制之命则无如何矣。矧其遗稿诗若文。汇为累帙者。残佚略尽。见藏于家。只七绝若干篇在耳。窃想当时不遇之赋。公不自为则必作于所与游。而若夫所俟之子云。至于今不值。死而有知。其不忞忞于斯也耶。公之玄孙翕。从余讲文事久矣。一日手公七绝稿。视余于可兴江上。戚然道公之遗事与稿本之存佚甚详。又曰。吾辈不肖甚。且弱丧流离。糊口于四方。唯此一束稿。亦不保其不灾于水火也。吾故不揆其力微。将与吾弟。刊之木以传于永久。然吾不敢知其必
悔窝集卷四 第 324L 页
 传与否。若子吾宗之有文者也。试为吾决之。苟以为可。则幸为之删定。而仍叙一言于卷首。俾后人得有以考信。则是死与生。并受子之赐也。如何。余固感秀才追先之思。而且以同出之义。不可辞也。遂受其稿而谨读之。虽寂寥短语。盖不足以尽作家之大全。然观其体裁浑成。真机溢发。得古诗人六义之遗。则全鼎之味。亦可以尝一脔而知之。尚何歉于完稿之不睹也。为之手正其脱讹。抄出最隽者六十八首。合为一编。而略缀所闻于秀才者如此。岂余足以当后世之子云。用纾公积恨之万一者耶。悲夫。秀才及其二弟。才性皆天得。又能刻意于学。不以穷厄堕其功。庶几能光其家烈者。
传与否。若子吾宗之有文者也。试为吾决之。苟以为可。则幸为之删定。而仍叙一言于卷首。俾后人得有以考信。则是死与生。并受子之赐也。如何。余固感秀才追先之思。而且以同出之义。不可辞也。遂受其稿而谨读之。虽寂寥短语。盖不足以尽作家之大全。然观其体裁浑成。真机溢发。得古诗人六义之遗。则全鼎之味。亦可以尝一脔而知之。尚何歉于完稿之不睹也。为之手正其脱讹。抄出最隽者六十八首。合为一编。而略缀所闻于秀才者如此。岂余足以当后世之子云。用纾公积恨之万一者耶。悲夫。秀才及其二弟。才性皆天得。又能刻意于学。不以穷厄堕其功。庶几能光其家烈者。辽沈关防考序
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况有国之壤地相界。风马牛日及焉。敌之生心不朝而暮者。其恶可忽之哉。全辽地方。固我邦之旧也。不知自何时折入于中国。至唐初。犹为高句丽之西鄙。则疑李绩之灭丽。即割以属之于幽蓟也。环山距海。烟火之域。千里而遥。惜乎。我失其利。而为他人有也。见今清奴首难于此。及主中土。而不敢忘本。则增浚积
悔窝集卷四 第 325H 页
 建州宁古塔。皆是也。丑运垂穷。馀种将捲还。则必当弱视我。欲肆其东噬之计。此正策士所宜深忧熟虑。不暇偷食之秋也。余过不自量。尝谓备豫之筹。莫先于明地利。故求得辽沈新图之自燕购来者。凡其远近山川大小州镇。与夫关防之险夷。道涂之迂直。无不反复究观。瞭然如身亲经行而目见之也。既而欲摹为他本。而力有不逮。则遂书其大槩而次第之。命之曰辽沈关防考。将与知者讲而明之。以裨 庙谟之万一。尝观韩文公画记。盖书以代画。而反详于画。其人物什器之属。不爽毫釐。可复画而无疑。真善记也。今以余之所述拟之于本境。未知其何如。而若其彷佛则有之。欲据此而复移于画。殆亦无难云。
建州宁古塔。皆是也。丑运垂穷。馀种将捲还。则必当弱视我。欲肆其东噬之计。此正策士所宜深忧熟虑。不暇偷食之秋也。余过不自量。尝谓备豫之筹。莫先于明地利。故求得辽沈新图之自燕购来者。凡其远近山川大小州镇。与夫关防之险夷。道涂之迂直。无不反复究观。瞭然如身亲经行而目见之也。既而欲摹为他本。而力有不逮。则遂书其大槩而次第之。命之曰辽沈关防考。将与知者讲而明之。以裨 庙谟之万一。尝观韩文公画记。盖书以代画。而反详于画。其人物什器之属。不爽毫釐。可复画而无疑。真善记也。今以余之所述拟之于本境。未知其何如。而若其彷佛则有之。欲据此而复移于画。殆亦无难云。石潭先生疏议抄序
才之作也。不万一二焉。才而学。学而成也。亦不万一二焉。学成而用。用而究于绩也。亦不万一二焉。三代以下。若贾谊,董仲舒,陆贽,韩愈,范仲淹,司马光,李纲玆若干人者。可谓才矣。然学则有歉。若二程及朱子。其于天德王道之学。可谓尽之矣。然厄于无时。卒不小用而止。此古来仁人志士所以屡发才难之叹。而尤戚戚于用舍行废之故者也。唯我石潭李先生。特
悔窝集卷四 第 3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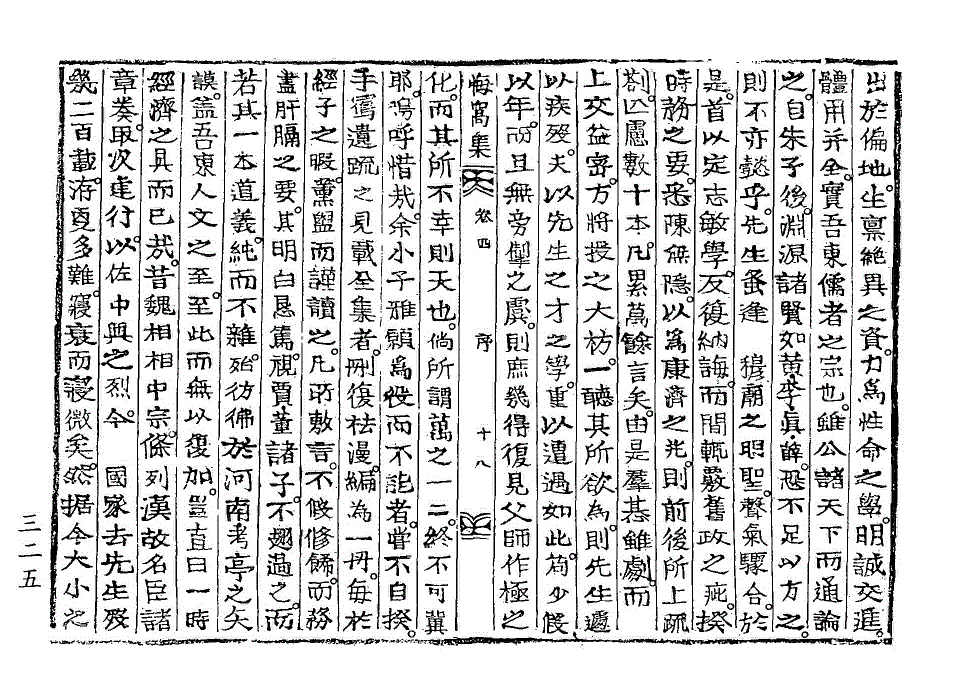 出于偏地。生禀绝异之资。力为性命之学。明诚交进。体用并全。实吾东儒者之宗也。虽公诸天下而通论之。自朱子后。渊源诸贤如黄,李,真,薛。恐不足以方之。则不亦懿乎。先生蚤逢 穆庙之明圣。声气骤合。于是。首以定志敏学。反复纳诲。而间辄覈旧政之疵。揆时务之要。悉陈无隐。以为康济之兆。则前后所上疏劄。亡虑数十本。凡累万馀言矣。由是群惎虽剧。而 上交益密。方将授之大枋。一听其所欲为。则先生遽以疾殁。夫以先生之才之学。重以遭遇如此。苟少假以年。而且无旁掣之虞。则庶几得复见父师作极之化。而其所不幸则天也。倘所谓万之一二。终不可冀耶。呜呼惜哉。余小子雅愿为役而不能者。尝不自揆。手写遗疏之见载全集者。删复祛漫。编为一册。每于经子之暇。薰盥而谨读之。凡所敷言。不假修饰。而务尽肝膈之要。其明白恳笃。视贾,董诸子。不翅过之。而若其一本道义。纯而不杂。殆彷佛于河南,考亭之矢谟。盖吾东人文之至。至此而无以复加。岂直曰一时经济之具而已哉。昔魏相相中宗。条列汉故名臣诸章奏。取次建行。以佐中兴之烈。今 国家去先生殁几二百载。荐更多难。寝衰而寝微矣。然据今大小之
出于偏地。生禀绝异之资。力为性命之学。明诚交进。体用并全。实吾东儒者之宗也。虽公诸天下而通论之。自朱子后。渊源诸贤如黄,李,真,薛。恐不足以方之。则不亦懿乎。先生蚤逢 穆庙之明圣。声气骤合。于是。首以定志敏学。反复纳诲。而间辄覈旧政之疵。揆时务之要。悉陈无隐。以为康济之兆。则前后所上疏劄。亡虑数十本。凡累万馀言矣。由是群惎虽剧。而 上交益密。方将授之大枋。一听其所欲为。则先生遽以疾殁。夫以先生之才之学。重以遭遇如此。苟少假以年。而且无旁掣之虞。则庶几得复见父师作极之化。而其所不幸则天也。倘所谓万之一二。终不可冀耶。呜呼惜哉。余小子雅愿为役而不能者。尝不自揆。手写遗疏之见载全集者。删复祛漫。编为一册。每于经子之暇。薰盥而谨读之。凡所敷言。不假修饰。而务尽肝膈之要。其明白恳笃。视贾,董诸子。不翅过之。而若其一本道义。纯而不杂。殆彷佛于河南,考亭之矢谟。盖吾东人文之至。至此而无以复加。岂直曰一时经济之具而已哉。昔魏相相中宗。条列汉故名臣诸章奏。取次建行。以佐中兴之烈。今 国家去先生殁几二百载。荐更多难。寝衰而寝微矣。然据今大小之悔窝集卷四 第 326H 页
 弊。溯流而求源。则固先生之所尝历指而为下救方者居多。然则是编也尽今日已疾之良剂也。其谁曰时变异宜。而不容复拟议也。但不知为先生之高平者。果有其人否乎。则是亦不可以万一二冀之者耶。呜呼欷矣。
弊。溯流而求源。则固先生之所尝历指而为下救方者居多。然则是编也尽今日已疾之良剂也。其谁曰时变异宜。而不容复拟议也。但不知为先生之高平者。果有其人否乎。则是亦不可以万一二冀之者耶。呜呼欷矣。古文百选集解序
始余之徙于东。为山水清雄。而土田多礼也。即所居之里。数岳相角立。大江屈折行其间。原隰方可十千亩。宜五谷桑麻。余甚乐而将老焉。既而得吾李君明夏。字晦叔甫。晦叔才气拔于人。博极天下书。与余游始浅而深。盖东偏之杰然特出者也。然晦叔学固博。而少为博士业所嬲夺。不暇专其功于古文章。俄举进士。年则三十几矣。遂用力于马,班,韩,欧诸作家。其覃思捷悟。月日骤进。而修辞之能。亦与之偕至矣。余喜其钟秀于峙融者固多。而其艺学之赡。殆若万稼之成于秋也。则余于是自贺其东徙之大有获也。近晦叔乃以其所解古文百选者授余曰。古之名能文者。自秦而洎汉,唐,宋盛矣。唯玆金文忠锡胄所选。尤属上品。吾于此将法古人结撰之至法。而亦欲使后蒙知所则也。以故据此而略采其佚遗。命以续编。且
悔窝集卷四 第 326L 页
 集诸家注说。粗释其句字之邃奥难晓者。又就其篇章。而猥标其体裁变化之槩。使其篇章句字大小之指。大都跃如焉。子之视之。以为如何。余谓凡注解之难有三。博识一难也。精思二难也。达辞三难也。盖识不博。则无以考古人所使之故实。思不精。则无以求其作述之常变。玆二者。或有能兼之矣。即所注之辞。无能达意。则又恶免使人䵝且惑也。今晦叔于此。既具三难。而无不给。又能广蒐诸家言而折衷之。可谓毫发无遗憾。而所以嘉惠后学诚大矣。若晦叔不暇自多。而将取法于此。则谦光之言也。然使晦叔及时反约。于此益自力焉。则游艺之大成。居可知也。是则余之所大获于东徙者。不特山水土田之为隽而已。其不足自贺者耶。
集诸家注说。粗释其句字之邃奥难晓者。又就其篇章。而猥标其体裁变化之槩。使其篇章句字大小之指。大都跃如焉。子之视之。以为如何。余谓凡注解之难有三。博识一难也。精思二难也。达辞三难也。盖识不博。则无以考古人所使之故实。思不精。则无以求其作述之常变。玆二者。或有能兼之矣。即所注之辞。无能达意。则又恶免使人䵝且惑也。今晦叔于此。既具三难。而无不给。又能广蒐诸家言而折衷之。可谓毫发无遗憾。而所以嘉惠后学诚大矣。若晦叔不暇自多。而将取法于此。则谦光之言也。然使晦叔及时反约。于此益自力焉。则游艺之大成。居可知也。是则余之所大获于东徙者。不特山水土田之为隽而已。其不足自贺者耶。读易琐识叙
古之为易之家多矣。言人人殊而易愈晦。自程叔子传之。朱子述本义。诸家皆废。易道遂大明于天下。其功可谓大矣。然夫易作于四圣。象数义理。先后渐备。故昊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孔子之十翼。总之为大成之典。乃程子首阐义理之隐微。而于象数则特置之。以遗后贤而分其功。是以朱子继之于后。因其成
悔窝集卷四 第 327H 页
 绪而并及其所未遑者。遂据四圣制作之次第。而各明其本旨。无有毫釐之或混或爽。于是乎象数之原始著。义理之奥益明。使卜筮得其用。学问知其方。即所谓与圣人为之译。而使程子而在者。亦必懑然服矣。此本义之所以并程传而为最完之书也。不以盛乎。余少子自弱岁。妄意于易学。始读本义。粗成其句读。厥后盖屡读屡思。历数十年。不敢辄废。然群疑如积。迄未能契悟。是虽困于蒙识。不足以与圣贤之能。抑亦其修辞至简。实未易于揆测故也。顷年以来。忧患与处。尤专意于研绎。而且进稽程传。旁究朱子诸说及其渊源诸子之疏。反覆参订。则向之积疑。稍得以释去。而第惧聪明日衰。随得而辄失之。则愚不自量。敢试剟缉诸要言之与本义实相发明者。用纸笔识之。间附以肤末之见。净写为一沓。题之曰读易琐识。常置之丌侧。要以取便于考阅而已。不敢以视之人也。然亦将以须蒙识之小进。而益事修改以弥吾年。窃庶几岁月之久。精专之至。而神或与通。卒得免于日用而不知云尔。
绪而并及其所未遑者。遂据四圣制作之次第。而各明其本旨。无有毫釐之或混或爽。于是乎象数之原始著。义理之奥益明。使卜筮得其用。学问知其方。即所谓与圣人为之译。而使程子而在者。亦必懑然服矣。此本义之所以并程传而为最完之书也。不以盛乎。余少子自弱岁。妄意于易学。始读本义。粗成其句读。厥后盖屡读屡思。历数十年。不敢辄废。然群疑如积。迄未能契悟。是虽困于蒙识。不足以与圣贤之能。抑亦其修辞至简。实未易于揆测故也。顷年以来。忧患与处。尤专意于研绎。而且进稽程传。旁究朱子诸说及其渊源诸子之疏。反覆参订。则向之积疑。稍得以释去。而第惧聪明日衰。随得而辄失之。则愚不自量。敢试剟缉诸要言之与本义实相发明者。用纸笔识之。间附以肤末之见。净写为一沓。题之曰读易琐识。常置之丌侧。要以取便于考阅而已。不敢以视之人也。然亦将以须蒙识之小进。而益事修改以弥吾年。窃庶几岁月之久。精专之至。而神或与通。卒得免于日用而不知云尔。送北评事李元亮(亮臣)序
夫士之能立大节取大名。而为一时所颙若者。常患
悔窝集卷四 第 3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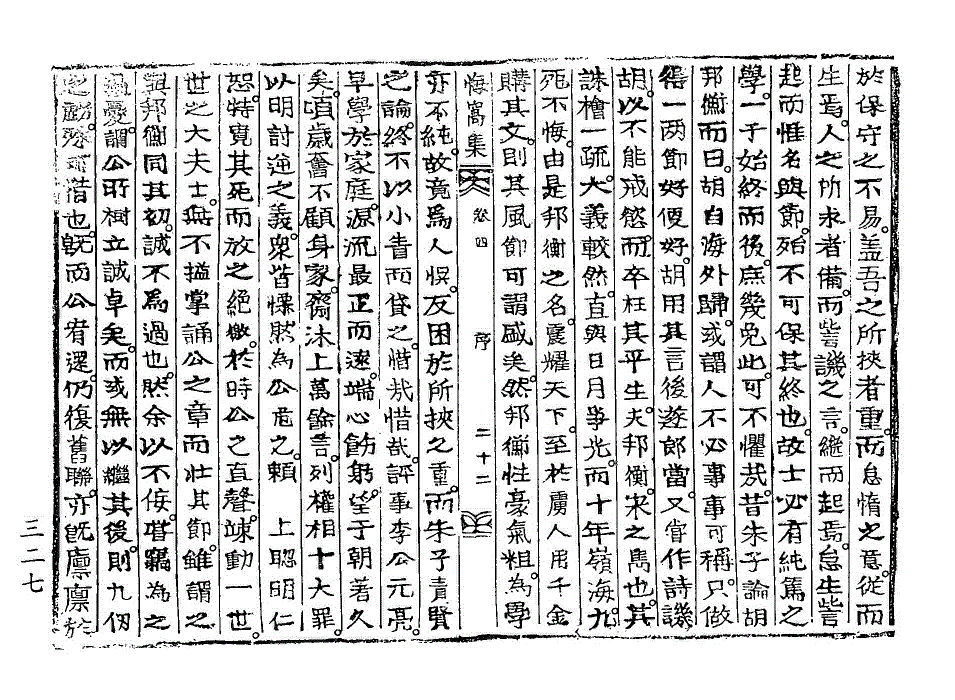 于保守之不易。盖吾之所挟者重。而怠惰之意。从而生焉。人之所求者备。而訾讥之言。继而起焉。怠生訾起而惟名与节。殆不可保其终也。故士必有纯笃之学。一于始终而后。庶几免此。可不惧哉。昔朱子论胡邦衡而曰。胡自海外归。或谓人不必事事可称。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胡用其言后遂郎当。又尝作诗讥胡。以不能戒欲。而卒枉其平生。夫邦衡。宋之隽也。其诛桧一疏。大义较然。直与日月争光。而十年岭海。九死不悔。由是邦衡之名。震耀天下。至于虏人用千金购其文。则其风节可谓盛矣。然邦衡性豪气粗。为学亦不纯。故竟为人误。反困于所挟之重。而朱子责贤之论。终不以小眚而贷之。惜哉惜哉。评事李公元亮。早学于家庭。源流最正而远。端心饬躬。望于朝著久矣。顷岁奋不顾身家。斋沐上万馀言。列权相十大罪。以明讨逆之义。众皆慄然为公危之。赖 上聪明仁恕。特宽其死而放之绝徼。于时公之直声。竦动一世。世之大夫士。无不扼掌诵公之章而壮其节。虽谓之与邦衡同其初。诚不为过也。然余以不佞。尝窃为之过忧。谓公所树立诚卓矣。而或无以继其后。则九仞之亏。殊可惜也。既而公宥还。仍复旧联。亦既廪廪于
于保守之不易。盖吾之所挟者重。而怠惰之意。从而生焉。人之所求者备。而訾讥之言。继而起焉。怠生訾起而惟名与节。殆不可保其终也。故士必有纯笃之学。一于始终而后。庶几免此。可不惧哉。昔朱子论胡邦衡而曰。胡自海外归。或谓人不必事事可称。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胡用其言后遂郎当。又尝作诗讥胡。以不能戒欲。而卒枉其平生。夫邦衡。宋之隽也。其诛桧一疏。大义较然。直与日月争光。而十年岭海。九死不悔。由是邦衡之名。震耀天下。至于虏人用千金购其文。则其风节可谓盛矣。然邦衡性豪气粗。为学亦不纯。故竟为人误。反困于所挟之重。而朱子责贤之论。终不以小眚而贷之。惜哉惜哉。评事李公元亮。早学于家庭。源流最正而远。端心饬躬。望于朝著久矣。顷岁奋不顾身家。斋沐上万馀言。列权相十大罪。以明讨逆之义。众皆慄然为公危之。赖 上聪明仁恕。特宽其死而放之绝徼。于时公之直声。竦动一世。世之大夫士。无不扼掌诵公之章而壮其节。虽谓之与邦衡同其初。诚不为过也。然余以不佞。尝窃为之过忧。谓公所树立诚卓矣。而或无以继其后。则九仞之亏。殊可惜也。既而公宥还。仍复旧联。亦既廪廪于悔窝集卷四 第 328H 页
 向用矣。而顾公屈强犹昔。不疚不惕。以故望实愈隆。人无间然。其所学之敦。所养之正。至是乃验。而彼邦衡之不克终。非所忧矣。虽然。险涂难尽。末俗易高。而或者流注之想。易失夬决之光。则亦不容不加意于学而究其极也。诗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此周人赠行之诗。而其所谓莫助。乃所以深助之也。公见为北出之役。徵言于余。余实知爱公者。敢诵玆诗。请为公行之赠。倘公不以人废之。而乃曰是惟君莫助之助也则幸矣。(元亮于其近戚。有可以苋陆戒者。)
向用矣。而顾公屈强犹昔。不疚不惕。以故望实愈隆。人无间然。其所学之敦。所养之正。至是乃验。而彼邦衡之不克终。非所忧矣。虽然。险涂难尽。末俗易高。而或者流注之想。易失夬决之光。则亦不容不加意于学而究其极也。诗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此周人赠行之诗。而其所谓莫助。乃所以深助之也。公见为北出之役。徵言于余。余实知爱公者。敢诵玆诗。请为公行之赠。倘公不以人废之。而乃曰是惟君莫助之助也则幸矣。(元亮于其近戚。有可以苋陆戒者。)春坊乙巳禊屏叙
故参判素窝赵公。晚遇不佞而辱交之。忘其年之先一饭而德与位之俱隆也。方其厄于时而屏处于忠原也。与余间一水而家。月日互造。为文酒之会。甚相驩也。间尝出一屏以视之曰。是吾乙巳春官春坊而得之者。坊之故事。凡遇册封入学等大典礼。诸僚之与事者。必为之作屏障之属以识喜。此则为 孝章邸下受封之庆而作者。而中之所绘列仙也。名于下。诸僚也。空其首。将以叙之也。既而无禄。 贰极上宾。吾每睹物思哀。涕不胜抆矣。识喜则已。而哀不可不识。子亦桂坊故属也。盍为吾志之。吾将手写而填于
悔窝集卷四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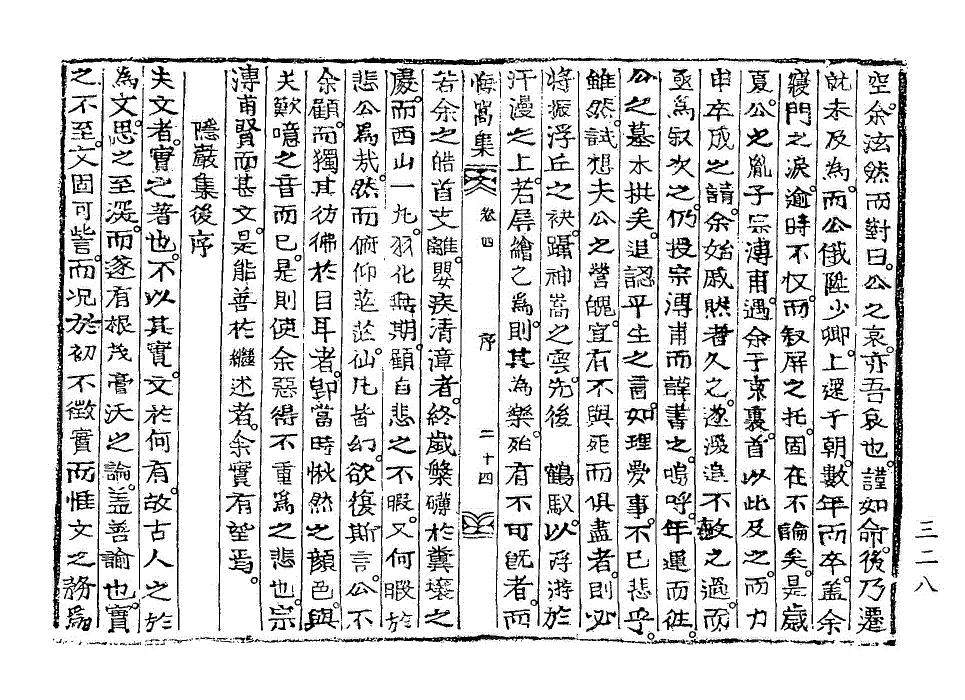 空。余泫然而对曰。公之哀。亦吾哀也。谨如命。后乃迁就未及为。而公俄升少卿。上还于朝。数年而卒。盖余寝门之泪。逾时不收。而叙屏之托。固在不论矣。是岁夏。公之胤子宗溥甫。遇余于京里。首以此及之。而力申卒成之请。余始戚然者久之。遂深追不敏之过。而亟为叙次之。仍授宗溥甫而谨书之。呜呼。年运而往。公之墓木拱矣。追认平生之言。如理梦事。不已悲乎。虽然。试想夫公之营魄。宜有不与死而俱尽者。则必将振浮丘之袂。蹑神嵩之云。先后 鹤驭。以浮游于汗漫之上。若屏绘之为。则其为乐。殆有不可既者。而若余之皓首支离。婴疾清漳者。终岁槃礴于粪壤之处。而西山一丸。羽化无期。顾自悲之不暇。又何暇于悲公为哉。然而俯仰茫茫。仙凡皆幻。欲复斯言。公不余顾。而独其彷佛于目耳者。即当时愀然之颜色。与夫叹噫之音而已。是则使余恶得不重为之悲也。宗溥甫贤而甚文。是能善于继述者。余实有望焉。
空。余泫然而对曰。公之哀。亦吾哀也。谨如命。后乃迁就未及为。而公俄升少卿。上还于朝。数年而卒。盖余寝门之泪。逾时不收。而叙屏之托。固在不论矣。是岁夏。公之胤子宗溥甫。遇余于京里。首以此及之。而力申卒成之请。余始戚然者久之。遂深追不敏之过。而亟为叙次之。仍授宗溥甫而谨书之。呜呼。年运而往。公之墓木拱矣。追认平生之言。如理梦事。不已悲乎。虽然。试想夫公之营魄。宜有不与死而俱尽者。则必将振浮丘之袂。蹑神嵩之云。先后 鹤驭。以浮游于汗漫之上。若屏绘之为。则其为乐。殆有不可既者。而若余之皓首支离。婴疾清漳者。终岁槃礴于粪壤之处。而西山一丸。羽化无期。顾自悲之不暇。又何暇于悲公为哉。然而俯仰茫茫。仙凡皆幻。欲复斯言。公不余顾。而独其彷佛于目耳者。即当时愀然之颜色。与夫叹噫之音而已。是则使余恶得不重为之悲也。宗溥甫贤而甚文。是能善于继述者。余实有望焉。隐岩集后序
夫文者。实之著也。不以其实。文于何有。故古人之于为文。思之至深。而遂有根茂膏沃之论。盖善谕也。实之不至。文固可訾。而况于初不徵实而惟文之务为
悔窝集卷四 第 329H 页
 者。则是亦剪䌽之肖花。鬼燐之拟火而已。岂足尚哉。三代之英。固无论已。若汉之贾董。唐宋之陆范李诸子。其文章之见存于天下者。譬如常食之可人。不容厌弃。虽其所学。不能无粹驳深浅之差。然其据实为文。不为空言剩辞之归。则未始不同也。先后累千馀年。凡以述作自名者。何可遽数。而彼皆冒华遗实。本之则无矣。故识者之所取在此而不在彼。盖文之尚实固如此也。故尚书隐岩李公。天赋至厚。笃于忠孝。而其为学盖本于六经。参以子史。既勤攻而富畜之矣。以故其发为文词。沛乎如恃源之水。一涉纸笔。顷刻千百言。不暇于字鍊句琢。而略无一二悬空之语。可谓有实斯有文矣。观其对策与奏疏十数通。无不恳款明畅。肝膈自出。若正君心。经世务。釐民事等诸言。殆可与谊,舒,敬舆相出入。而末年若干本之论城守便宜。则实符于文正,忠定之确见。所以当时屡荷 圣考之嘉奖。不翅如汉,唐诸君之各贤其臣者。而或者惜其言之不尽见用于时也。此岂工为华藻。无适于施用者之比也哉。盖公殁后二十馀年。公之孙奎臣等。将刊行遗集。以小子蒙公谕诲有素。责以删定之役。而且徵卷后之识。义不敢以不能辞也。谨受
者。则是亦剪䌽之肖花。鬼燐之拟火而已。岂足尚哉。三代之英。固无论已。若汉之贾董。唐宋之陆范李诸子。其文章之见存于天下者。譬如常食之可人。不容厌弃。虽其所学。不能无粹驳深浅之差。然其据实为文。不为空言剩辞之归。则未始不同也。先后累千馀年。凡以述作自名者。何可遽数。而彼皆冒华遗实。本之则无矣。故识者之所取在此而不在彼。盖文之尚实固如此也。故尚书隐岩李公。天赋至厚。笃于忠孝。而其为学盖本于六经。参以子史。既勤攻而富畜之矣。以故其发为文词。沛乎如恃源之水。一涉纸笔。顷刻千百言。不暇于字鍊句琢。而略无一二悬空之语。可谓有实斯有文矣。观其对策与奏疏十数通。无不恳款明畅。肝膈自出。若正君心。经世务。釐民事等诸言。殆可与谊,舒,敬舆相出入。而末年若干本之论城守便宜。则实符于文正,忠定之确见。所以当时屡荷 圣考之嘉奖。不翅如汉,唐诸君之各贤其臣者。而或者惜其言之不尽见用于时也。此岂工为华藻。无适于施用者之比也哉。盖公殁后二十馀年。公之孙奎臣等。将刊行遗集。以小子蒙公谕诲有素。责以删定之役。而且徵卷后之识。义不敢以不能辞也。谨受悔窝集卷四 第 329L 页
 而卒业。而书此以复之。若夫歌诗之作。公固不屑而未尝用力。然而直写性情。不失温厚之旨。亦可以见其所存之槩矣。文之删仅十二三。诗则倍之。凡为集几卷。
而卒业。而书此以复之。若夫歌诗之作。公固不屑而未尝用力。然而直写性情。不失温厚之旨。亦可以见其所存之槩矣。文之删仅十二三。诗则倍之。凡为集几卷。赠田生(祥顼)东归序
仙槎田生。橐数旬粮。一僮一骑。踰重岭涉大川。七日而抵横城县。顾余于僦舍。始接即知为隽士也。劳谢毕。乃问其所以来者。生曰。吾地濒海荒远。文献无素。盖陋邦也。幸而华阳宋先生,黄江权先生。尝取次游过。则乡人士之觌德而闻风者。至今山仰。皆有所奋兴之志。烝民首章之云。诚不可诬也。始吾父倡于乡议。作院宇以奉两先生遗像。且为群子弟静修之所。诸同志者。无不悦从。则又就谋于荐绅诸公。皆蒙其开可。于是。相地于县治之东玉溪里。遂合群力。贸财佣工。几于有成。然役丁与食。不容不仰于县官。而吾守不见听。故吾父使不肖。往控于道伯及原牧及横守。横守。即黄江门徒也。吾故径走至此。将丐其大出力以助。且发书以绍介于伯牧及旁郡县也。余曰。凡院宇之叠营。自 朝家申禁。而士大夫多非斥者。恐君行徒劳无益也。既而生见守。守果坚拒。所谒皆不
悔窝集卷四 第 330H 页
 售。生困且恚。即旋马而归。谓余曰。闻子之有文久矣。愿为吾赠一言。使吾获免于虚还也。余为之懑然。乃言曰。夫院宇之刱。上以谨崇奉。下以备藏修。其为制固美矣。然比年以来。所在争置。其敝多端。一人之祠。或遍八路。一也。多占氓户。耗减兵额。二也。滥推朝贵为山长。倚其气势。反灭学校。使尊卑倒置。三也。土豪子姓。未尝攻业而惟私岁入。以供醉饫之费。四也。或阿所好。或媚后承。不问道德之高下有无。猥奉俎豆。相师成俗。五也。视为利窟。冒死争夺。无异于市井驵𩦱。大坏礼让之风。六也。凡玆六弊。特其大者。馀不可遽数。则 朝禁之申严。公议之讥斥。固其所也。虽然。见今异教不息。其为害烈于猛洪。而其宫室之僭拟王居者。不翅百倍于儒院。乃不知抑彼而惟此之欲沮。何哉。此朱夫子所以深慨于鹿洞者也。而况仙槎最是天荒之地。区区举人之业。犹且堇有焉。又何望于向上事耶。今乘其观感之机。而亟有以激厉之。遂使舍旧而即新可也。岂可限以著令。不复奖许。用尼其兴起之心哉。若贵守与横守。所谓胶固而不知变者也。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伯牧他守。未必皆如二守之为。君其历干不置。则宜必有所遇。而或不至于
售。生困且恚。即旋马而归。谓余曰。闻子之有文久矣。愿为吾赠一言。使吾获免于虚还也。余为之懑然。乃言曰。夫院宇之刱。上以谨崇奉。下以备藏修。其为制固美矣。然比年以来。所在争置。其敝多端。一人之祠。或遍八路。一也。多占氓户。耗减兵额。二也。滥推朝贵为山长。倚其气势。反灭学校。使尊卑倒置。三也。土豪子姓。未尝攻业而惟私岁入。以供醉饫之费。四也。或阿所好。或媚后承。不问道德之高下有无。猥奉俎豆。相师成俗。五也。视为利窟。冒死争夺。无异于市井驵𩦱。大坏礼让之风。六也。凡玆六弊。特其大者。馀不可遽数。则 朝禁之申严。公议之讥斥。固其所也。虽然。见今异教不息。其为害烈于猛洪。而其宫室之僭拟王居者。不翅百倍于儒院。乃不知抑彼而惟此之欲沮。何哉。此朱夫子所以深慨于鹿洞者也。而况仙槎最是天荒之地。区区举人之业。犹且堇有焉。又何望于向上事耶。今乘其观感之机。而亟有以激厉之。遂使舍旧而即新可也。岂可限以著令。不复奖许。用尼其兴起之心哉。若贵守与横守。所谓胶固而不知变者也。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伯牧他守。未必皆如二守之为。君其历干不置。则宜必有所遇。而或不至于悔窝集卷四 第 330L 页
 落莫矣。又何用悻悻然遽归为哉。抑余有欲特勉者。夫士之为学。惟在读书诵诗。讲明此道体之吾身。则不待外求而有馀裕矣。是所谓尊信前哲之至也。若庙宇之严饰。香火之虔奉。外也非内也。佛书亦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倘君之父子。真慕两先生之道学。要为乡邦之善士。则恐不若急其内而缓其外也。幸君无以余耄而略其言。归告尊府而力图之也。
落莫矣。又何用悻悻然遽归为哉。抑余有欲特勉者。夫士之为学。惟在读书诵诗。讲明此道体之吾身。则不待外求而有馀裕矣。是所谓尊信前哲之至也。若庙宇之严饰。香火之虔奉。外也非内也。佛书亦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倘君之父子。真慕两先生之道学。要为乡邦之善士。则恐不若急其内而缓其外也。幸君无以余耄而略其言。归告尊府而力图之也。耘谷诗集叙
近世有名儒。以前朝之郑圃隐梦周,吉冶隐再,元耘谷天锡为三仁。众皆允之无异辞。然余尝读丽季究论三仁之本末。宜亦有不可苟者。盖圃隐力抗大难。卒以死继。诚烈矣。然其始仕。实当妖旽时。且于祦,昌之死。参盟策勋。此其志。惟以宗社为重。将欲隐忍而就事。然人臣之义。王陵为正。则石潭李文成公。只予其忠而不予其尽道是也。冶隐始就晋涂。见险能止。终又不二其心。固特操也。然其拜笺称臣。君子或病之。惟耘谷先生。初既不立于乱朝。及其亡也。以布衣自靖。没身穷谷。彼伯夷之守饿。元亮之全贞。恐无以过之。是岂圃,冶二公所能比拟者哉。先生字某。原州
悔窝集卷四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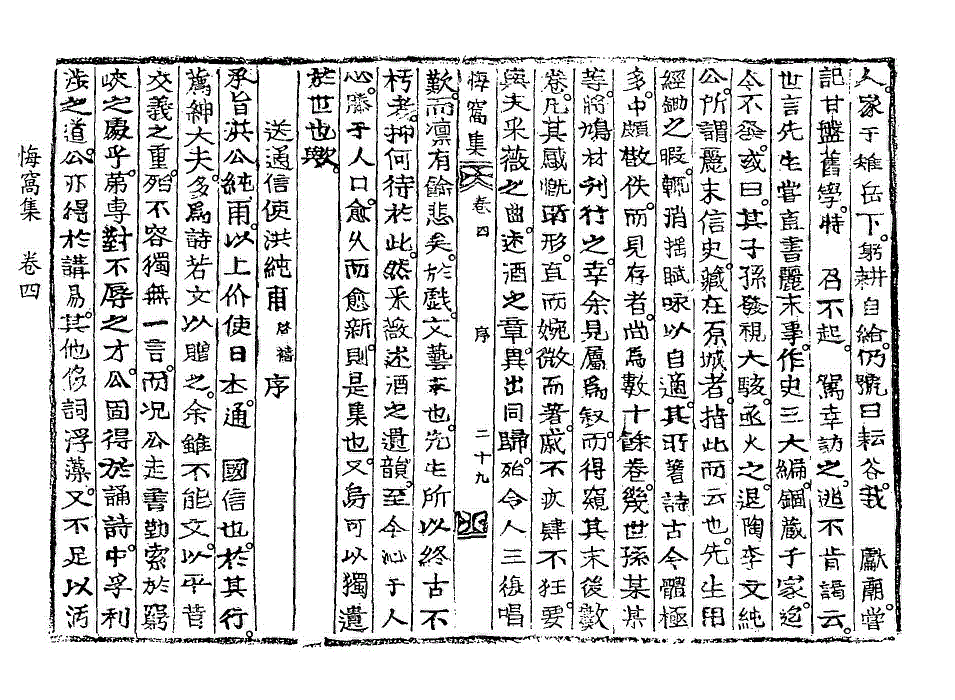 人。家于雉岳下。躬耕自给。仍号曰耘谷。我 献庙。尝记甘盘旧学。特 召不起。 驾幸访之。逃不肯谒云。世言先生尝直书丽末事。作史三大编。锢藏于家。迄今不发。或曰。其子孙发视大骇。亟火之。退陶李文纯公。所谓丽末信史。藏在原城者。指此而云也。先生用经锄之暇。辄消摇赋咏以自适。其所著诗古今体极多。中颇散佚。而见存者。尚为数十馀卷。几世孙某某等。将鸠材刊行之。幸余见属为叙。而得窥其末后数卷。凡其感慨所形。直而婉微而著。戚不疚肆不狂。要与夫采薇之曲。述酒之章。异出同归。殆令人三复唱叹。而凛有馀悲矣。于戏。文艺末也。先生所以终古不朽者。抑何待于此。然采薇述酒之遗韵。至今沁于人心。滕于人口。愈久而愈新。则是集也。又乌可以独遗于世也欤。
人。家于雉岳下。躬耕自给。仍号曰耘谷。我 献庙。尝记甘盘旧学。特 召不起。 驾幸访之。逃不肯谒云。世言先生尝直书丽末事。作史三大编。锢藏于家。迄今不发。或曰。其子孙发视大骇。亟火之。退陶李文纯公。所谓丽末信史。藏在原城者。指此而云也。先生用经锄之暇。辄消摇赋咏以自适。其所著诗古今体极多。中颇散佚。而见存者。尚为数十馀卷。几世孙某某等。将鸠材刊行之。幸余见属为叙。而得窥其末后数卷。凡其感慨所形。直而婉微而著。戚不疚肆不狂。要与夫采薇之曲。述酒之章。异出同归。殆令人三复唱叹。而凛有馀悲矣。于戏。文艺末也。先生所以终古不朽者。抑何待于此。然采薇述酒之遗韵。至今沁于人心。滕于人口。愈久而愈新。则是集也。又乌可以独遗于世也欤。送通信使洪纯甫(启禧)序
承旨洪公纯甫。以上价使日本。通 国信也。于其行。荐绅大夫。多为诗若文以赠之。余虽不能文。以平昔交义之重。殆不容独无一言。而况公走书勤索于穷峡之处乎。第专对不辱之才。公固得于诵诗。中孚利涉之道。公亦得于讲易。其他侈词浮藻。又不足以污
悔窝集卷四 第 331L 页
 盛橐。则余将何言而可哉。然窃独有一二事之欲谒者。夫 本朝之许倭和。今已百有五十年。而南溟万里涛澜不惊。此盖 本朝之礼义威信。大有以慑其气而服其心也。然而世运之消息有数。国势之盛衰不常。乃今文武不才。姑息是事。内而无折冲之具。外而无固圉之备。则彼狡焉旁睨者之毕竟不贰。其可保乎。此识者所以深忧而切虑也。是行也。以公之机鉴。必有以善觇其情形而归。然情微瞹而难测。形变幻而易眩。惟煞用心力。然后乃能得其真也。或者云信使之职。不过操幤申好而已。又安用觇察为哉。事或宣露。不几于招拂而生衅耶。余谓不然。春秋列国。如齐晋鲁宋之属。非兄弟则舅甥也。然其大夫之交聘。歌乐合欢之外。犹不废刺取之事。未闻其以此而失好也。况彼奴之于我。其初仇雠耳。是乌可一切相信而不复虞哉。礼以接之。智以诇之。斯其宜也。公以为如何。且日本其地未详方所。从前行李之说。皆曰泛针船上。常指莱州之东南。姜沆看羊录则曰。据倭人之言。疑在我国之东北。与稳庆等地相直。而王弇州集。倭寇必以东北风。来犯浙东。东北风。每盛于清明重阳两节后。故中国之防倭。以四五月为大汛。九
盛橐。则余将何言而可哉。然窃独有一二事之欲谒者。夫 本朝之许倭和。今已百有五十年。而南溟万里涛澜不惊。此盖 本朝之礼义威信。大有以慑其气而服其心也。然而世运之消息有数。国势之盛衰不常。乃今文武不才。姑息是事。内而无折冲之具。外而无固圉之备。则彼狡焉旁睨者之毕竟不贰。其可保乎。此识者所以深忧而切虑也。是行也。以公之机鉴。必有以善觇其情形而归。然情微瞹而难测。形变幻而易眩。惟煞用心力。然后乃能得其真也。或者云信使之职。不过操幤申好而已。又安用觇察为哉。事或宣露。不几于招拂而生衅耶。余谓不然。春秋列国。如齐晋鲁宋之属。非兄弟则舅甥也。然其大夫之交聘。歌乐合欢之外。犹不废刺取之事。未闻其以此而失好也。况彼奴之于我。其初仇雠耳。是乌可一切相信而不复虞哉。礼以接之。智以诇之。斯其宜也。公以为如何。且日本其地未详方所。从前行李之说。皆曰泛针船上。常指莱州之东南。姜沆看羊录则曰。据倭人之言。疑在我国之东北。与稳庆等地相直。而王弇州集。倭寇必以东北风。来犯浙东。东北风。每盛于清明重阳两节后。故中国之防倭。以四五月为大汛。九悔窝集卷四 第 332H 页
 十月为小汛。以此推之。其国正在中国与我邦之东北。而姜录信矣。国俗卤莽。先后使航之过海者凡几何。而迄不知其地之适当何方。夫欲备风寒。必知其所自来。矧乎欲备寇难。而莫知其所自来可乎。幸公考其图志。揆以日晷。必知其处。以破吾人积久之惑。则亦一快也。昔郑圃隐,黄秋浦二公。皆为是役。其清风迈气。惊动异俗。至今见诵。余固知公之贤。必能继其后也。故区区私祝。不敢复烦云。
十月为小汛。以此推之。其国正在中国与我邦之东北。而姜录信矣。国俗卤莽。先后使航之过海者凡几何。而迄不知其地之适当何方。夫欲备风寒。必知其所自来。矧乎欲备寇难。而莫知其所自来可乎。幸公考其图志。揆以日晷。必知其处。以破吾人积久之惑。则亦一快也。昔郑圃隐,黄秋浦二公。皆为是役。其清风迈气。惊动异俗。至今见诵。余固知公之贤。必能继其后也。故区区私祝。不敢复烦云。悔窝集卷四
题跋
追惜锡翰诗跋
右追惜兄子锡翰诗一绝。翰。吾仲氏藐屋翁之才子也。生聪悟。勤于学。志又不凡。近吾则爱而畏之。不幸天与其至粹而夺之。寿未及冠。以病夭。恸矣哉。吾家儒也。先公以经学文章教于家。仲氏自早岁。专于为己之学。翰也盖生于道艺之囿。耳目所擩染。皆是物也。性又嗜学。甫总发。日啖群书。不翅如馋口之遇肥腯。自此数年。博通广记。才与身长。尤好覃思于经若史。必穷其隐奥之义。不欲一二遗也。吾尝读易于龙岳书室。旁究启蒙蓍卦之图说。以及星历律算之书。积用心力。粗能会通。翰一游目而辄识其槩。且吾观
悔窝集卷四 第 332L 页
 历代史。必参伍反覆于治乱兴坏善败之故。礼乐刑政兵徭之制。而至如英伟沈鸷之士之运谋决机处。尤费揣摩。翰常上下其论。明识英辩。类多契吾见者。间遇哲人君子忧违而不自见者。吾必掩卷累叹。翰亦忾然咨嗟。深识吾之几微。吾以素钝滞。不娴于举业。而且有所不屑焉。将须静致学以从所好。而翰虽弱龄。实同此志。步趍相从。不及不止。而至于超轶处。殆欲先之。苟非得于天者英粹绝伦。则其能若此耶。向使并与年而得之。肆其志之所欲。而以究于成。则必有过于人者。而不能然。可胜惜哉。虽然。运气方消。所讳者才。翰也不年。亦其宜也。呜呼惜哉。
历代史。必参伍反覆于治乱兴坏善败之故。礼乐刑政兵徭之制。而至如英伟沈鸷之士之运谋决机处。尤费揣摩。翰常上下其论。明识英辩。类多契吾见者。间遇哲人君子忧违而不自见者。吾必掩卷累叹。翰亦忾然咨嗟。深识吾之几微。吾以素钝滞。不娴于举业。而且有所不屑焉。将须静致学以从所好。而翰虽弱龄。实同此志。步趍相从。不及不止。而至于超轶处。殆欲先之。苟非得于天者英粹绝伦。则其能若此耶。向使并与年而得之。肆其志之所欲。而以究于成。则必有过于人者。而不能然。可胜惜哉。虽然。运气方消。所讳者才。翰也不年。亦其宜也。呜呼惜哉。题九龙瀑帖
画不必一切形似。在得其意而已。庚子初夏。余入枫岳。观于水。得九龙瀑甚壮之。归与郑殿中元伯语其槩。元伯喜为水墨戏者。闻之耸然。从坐上洒笔。直就之。便见千尺奇势。宛然本境。快矣哉。但风沫冥濛。全洞常雨之状。略不尽其变。然大意尽好。不必苛论也。至岳之大体。元伯亦尝见而画之矣。然所谓万二千峰。远近蔽亏。不可尽摹。若一切刊去。独为毗卢一顶。以临天下。岂不杰然大观。余尤听听。而元伯辞以倦
悔窝集卷四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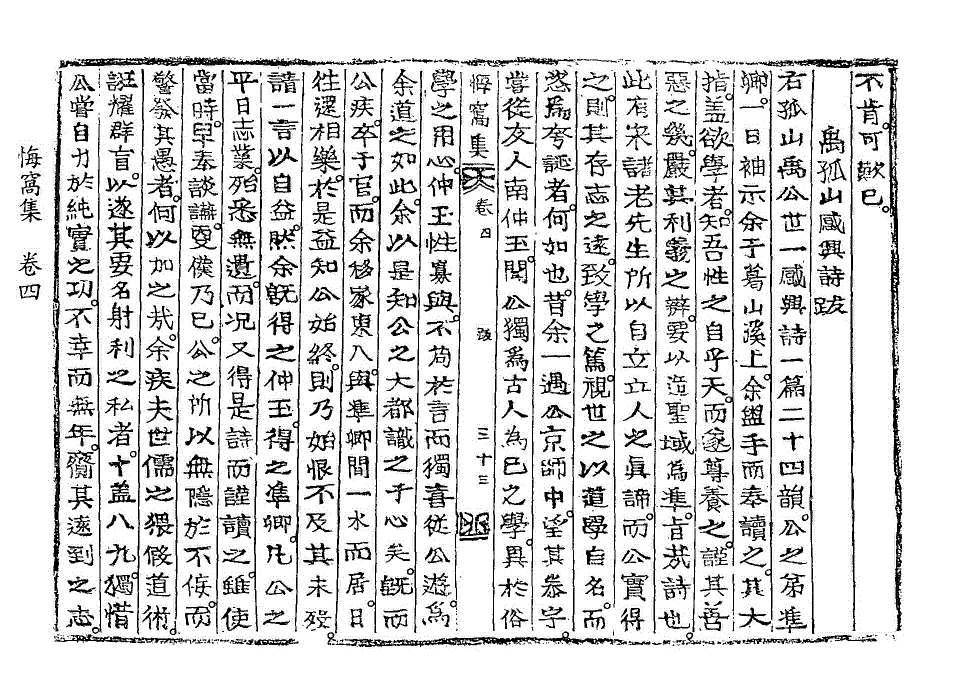 不肯。可叹已。
不肯。可叹已。禹孤山感兴诗跋
右孤山禹公世一感兴诗一篇二十四韵。公之弟准卿。一日袖示余于葛山溪上。余盥手而奉读之。其大指。盖欲学者。知吾性之自乎天。而遂尊养之。谨其善恶之几。严其利义之辨。要以造圣域为准。旨哉诗也。此有宋诸老先生所以自立立人之真谛。而公实得之。则其存志之远。致学之笃。视世之以道学自名。而恣为夸诞者。何如也。昔余一遇公京师中。望其泰宇。尝从友人南仲玉。闻公独为古人为己之学。异于俗学之用心。仲玉性寡与。不苟于言而独喜从公游。为余道之如此。余以是知公之大都识之于心矣。既而公疾。卒于官。而余移家东入。与准卿间一水而居。日往还相乐。于是益知公始终。则乃始恨不及其未殁。请一言以自益。然余既得之仲玉。得之准卿。凡公之平日志业。殆悉无遗。而况又得是诗而谨读之。虽使当时。早奉谈宴。更仆乃已。公之所以无隐于不佞。而警发其愚者。何以加之哉。余疾夫世儒之猥假道术。诳耀群盲。以遂其要名射利之私者。十盖八九。独惜公尝自力于纯实之功。不幸而无年。赍其远到之志。
悔窝集卷四 第 333L 页
 未能卒究。则为之三复是诗。而不觉累叹也。遂忘其狂率。略识其末简。以诒来学。余亦以自励焉。公丹山人。早从事于权遂庵之门。其渊源最远。且深于易学云。
未能卒究。则为之三复是诗。而不觉累叹也。遂忘其狂率。略识其末简。以诒来学。余亦以自励焉。公丹山人。早从事于权遂庵之门。其渊源最远。且深于易学云。书韩文公潮州谢上表后
凡不韪之言若事。不惟皆小人者为之。君子盖亦有不知而为者。过也非恶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故君子之过。固圣人之所必恕。而其所不恕而必以诛者。乃小人之恶。既知而故为者也。余读韩文公潮州谢表。既谢其屈刑章。畀禄食。为恩甚大。则亦可已矣不容已。而忧其衰疾孤危之躯。远拘恶地。风鱼瘴疠。日夕为患。必死而不可还。则以此乞哀。亦无不可也。至于自荐其文章。可使论述功德。刻之琬琰。藏于岱宗。继又盛言天子武功文德。可比祖宗除治之烈而直过之。劝以遄封告成。而自伤投荒濒死。不得效薄技于嘉会。此其言不几于阿邑人主之意。而且衒其能。阴欲以早脱海岛之囚者耶。故后之君子。辄以此病公。而虽使知慕公者善为之辞。亦不能分解矣。虽然。此乃公未始知封禅之为君举之谬。而臣子之劝之也。为纳谀之尤。则只循故事而为之矣。其失
悔窝集卷四 第 334H 页
 虽大。要亦君子之过。而不可以小人逢迎之恶。比而同之也。夫封禅。非古谊也。恶有贤圣之君。自多其功。用以夸耀于天下后世也。而况不德而为此。则适足以欺诬神人。贻不赀之笑而已。盖其事始刱于秦政,汉彻。自圣好大之君也。而抑当时丞相御史将军郎官博士之属。相率而建议。皆以为帝王之盛节。莫过于此。乃妄引隆古神圣之有事于名山者。七十有二君。而又摭舜典东狩柴望之文。以傅会其义。若秦之李斯,卢生。汉之相如,儿宽,太史迁。是也。而以儒学自名。如董仲舒,刘向,杨雄。亦未始论其纰谬。而或从而赞美之。是故。以光武之明。其始拒群臣之请也。不曰封禅故不可以。唯曰吾德之未至。既而杀其礼而终行之。唐之文皇。亦尝谦让。而卒不能胜其欲。则赖魏徵之进谏。遂寝东巡之驾矣。然徵之谏。亦不论其是非。而惟以劳费为言。文皇之所以寝之。亦以此焉。向使关东不饥。而供亿有裕。则徵亦无辞于谏止。而文皇亦必踵秦,汉之封矣。顾其事。虽始于好大之君为之愚首。而既历名臣巨儒之傅会曲成而称道之不已。则虽以贤君硕辅之间出者。亦不免于歆艳而尊述之。使其功烈。略有可纪。则君而行之不知汰。臣而
虽大。要亦君子之过。而不可以小人逢迎之恶。比而同之也。夫封禅。非古谊也。恶有贤圣之君。自多其功。用以夸耀于天下后世也。而况不德而为此。则适足以欺诬神人。贻不赀之笑而已。盖其事始刱于秦政,汉彻。自圣好大之君也。而抑当时丞相御史将军郎官博士之属。相率而建议。皆以为帝王之盛节。莫过于此。乃妄引隆古神圣之有事于名山者。七十有二君。而又摭舜典东狩柴望之文。以傅会其义。若秦之李斯,卢生。汉之相如,儿宽,太史迁。是也。而以儒学自名。如董仲舒,刘向,杨雄。亦未始论其纰谬。而或从而赞美之。是故。以光武之明。其始拒群臣之请也。不曰封禅故不可以。唯曰吾德之未至。既而杀其礼而终行之。唐之文皇。亦尝谦让。而卒不能胜其欲。则赖魏徵之进谏。遂寝东巡之驾矣。然徵之谏。亦不论其是非。而惟以劳费为言。文皇之所以寝之。亦以此焉。向使关东不饥。而供亿有裕。则徵亦无辞于谏止。而文皇亦必踵秦,汉之封矣。顾其事。虽始于好大之君为之愚首。而既历名臣巨儒之傅会曲成而称道之不已。则虽以贤君硕辅之间出者。亦不免于歆艳而尊述之。使其功烈。略有可纪。则君而行之不知汰。臣而悔窝集卷四 第 334L 页
 赞之不知谄。其风已成。往而不反。直至有宋诸贤之正论出。然后人人始知其为大不韪也。文公之学。盖君子而未至者。出于秦汉之后。而先于有宋之诸贤。未尝有闻于大居正之义。而乃蔽于长卿,子云辈张皇之说。则又恶知以是导君之为谄首也。槩亦据其君之成烈。较之古先帝王。殆亦无愧于介丘之有事者。故为之劝之。而初非切切于逢君而干泽也。故曰其过虽大。要不过为不知之过。而非小人故为之恶也。或疑公初不知封禅之非古谊。而惟知尊其君。欲其章显于久载者。则何不于平淮之初。赞以成之。及至刺潮之后。乃是汲汲焉附谢表以请欤。考其始则缓于尊君之诚。要其后则近于谄上之风。公必居一于此矣。曰。是不然。公之在朝也。宪宗之武烈未终。而公虽始衰。顾未有死不及事之虑矣。及贬于潮。困于炎瘴。逼于忧患。诚恐一朝溘死。莫睹大典之举。而且其茂陵颂德之文。非我谁复作之者。故不暇于君伐之。待其终而露表以劝之。兼荐其文章之能而不自嫌。是岂缓于陈诚者耶。且使公早知其言之不免于不韪。公虽没身不宥。埋骨于瘴海之濒。亦不肯为此。何者。盖公学虽未至。而其所存者正直不回。深疾鄙
赞之不知谄。其风已成。往而不反。直至有宋诸贤之正论出。然后人人始知其为大不韪也。文公之学。盖君子而未至者。出于秦汉之后。而先于有宋之诸贤。未尝有闻于大居正之义。而乃蔽于长卿,子云辈张皇之说。则又恶知以是导君之为谄首也。槩亦据其君之成烈。较之古先帝王。殆亦无愧于介丘之有事者。故为之劝之。而初非切切于逢君而干泽也。故曰其过虽大。要不过为不知之过。而非小人故为之恶也。或疑公初不知封禅之非古谊。而惟知尊其君。欲其章显于久载者。则何不于平淮之初。赞以成之。及至刺潮之后。乃是汲汲焉附谢表以请欤。考其始则缓于尊君之诚。要其后则近于谄上之风。公必居一于此矣。曰。是不然。公之在朝也。宪宗之武烈未终。而公虽始衰。顾未有死不及事之虑矣。及贬于潮。困于炎瘴。逼于忧患。诚恐一朝溘死。莫睹大典之举。而且其茂陵颂德之文。非我谁复作之者。故不暇于君伐之。待其终而露表以劝之。兼荐其文章之能而不自嫌。是岂缓于陈诚者耶。且使公早知其言之不免于不韪。公虽没身不宥。埋骨于瘴海之濒。亦不肯为此。何者。盖公学虽未至。而其所存者正直不回。深疾鄙悔窝集卷四 第 335H 页
 夫小人之为者也。故既论凶秽之骨。不宜供迎。而宜投之水火。轻犯人主不测之怒。而不之顾。且不奉后命。疾驱入魏。面诘庭凑之罪。视白刃如无顾。公之轻生而重义如此。其肯效尤于怂恿逢迎之态也哉。虽然。君子学贵明善。学不能明善。而遽欲立人之朝。以之发言建事。不谬于臧否者实难。使公早得从事于穷格之功。以要其学之大全而不迷于是非之实。则如封禅之非古谊而为君举之大谬者。岂不能早辨于当时。而必俟夫宋贤之后出也哉。惜哉惜哉。嗟呼凡人君好大之弥文。岂惟封禅而已。而既经诸儒贤之论斥。明载纪籍者。盖亦多矣。彼为人臣而具视听者。其孰不知之。然而或敢肆然倡声于庭。不少顾惮。其稍欲自好者。始顾名义之重。为之裴徊前却。而卒不敢独异焉。既以猥引韩公之事。文其外曰。如公之贤。亦不免有过。况于吾辈乎。此皆小人故为之恶也。传所谓逢君之大夫。其罪大者。可胜诛哉。
夫小人之为者也。故既论凶秽之骨。不宜供迎。而宜投之水火。轻犯人主不测之怒。而不之顾。且不奉后命。疾驱入魏。面诘庭凑之罪。视白刃如无顾。公之轻生而重义如此。其肯效尤于怂恿逢迎之态也哉。虽然。君子学贵明善。学不能明善。而遽欲立人之朝。以之发言建事。不谬于臧否者实难。使公早得从事于穷格之功。以要其学之大全而不迷于是非之实。则如封禅之非古谊而为君举之大谬者。岂不能早辨于当时。而必俟夫宋贤之后出也哉。惜哉惜哉。嗟呼凡人君好大之弥文。岂惟封禅而已。而既经诸儒贤之论斥。明载纪籍者。盖亦多矣。彼为人臣而具视听者。其孰不知之。然而或敢肆然倡声于庭。不少顾惮。其稍欲自好者。始顾名义之重。为之裴徊前却。而卒不敢独异焉。既以猥引韩公之事。文其外曰。如公之贤。亦不免有过。况于吾辈乎。此皆小人故为之恶也。传所谓逢君之大夫。其罪大者。可胜诛哉。书钱虞山有学集
夫治平之音。安乐冲旷。乱亡之音。悲愤切蹙。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尚矣。文章之于音乐。实同源流。则其随世嬗变。亦宜也。然吾夫子当周之衰。其十翼春秋之
悔窝集卷四 第 335L 页
 作。洎夫龟山猗兰之操。未始与典谟之体。韶咸之音殊科。回之琴。点之瑟。洋洋盈耳。搏拊升歌之遗故在。而且柴桑幽士。其词澹然以平。燕狱羁囚。其文肆然以豪。斯其世何世也。岂天地间正气中声。初未尝尧存桀亡。而乃与夫不死之人心。交贯互宣。为雅乐为粹词。而不容已耶。然则恶在政也。亦视其人之何如耳。钱虞山有学集出于 明后。余观其诗若文。大都气轻而促。言戚而厖。哀之固也。何其泥也耶。尝考 皇朝遗史。虞山其人。虽以东林之淑类称。而所性儇躁。矜其小慧。闇于大道。于其阁讼。可见侏儒之一节矣。而况尝位大臣之列。而不能一死于国破君亡之馀。落发披条。窜身丛林。此其心之先身而死久矣。是安得不易乎世而卓然自立者耶。故其文澜才燄。虽王长当世。自以高出 本朝。远绍唐,宋。而卒与夫水调八破之流。烂熳同归也无怪矣。呜呼。彼固不祥之人。而词又不祥之音也。谓宜斥以远之。惟恐或似而顾今之人。方且赏爱之拟议之。惟恐其不能似也。抑又何也。岂其文澜才焰。能使人易眩耶。将时变所渐。有不约而同者存耶。呜呼殆矣。
作。洎夫龟山猗兰之操。未始与典谟之体。韶咸之音殊科。回之琴。点之瑟。洋洋盈耳。搏拊升歌之遗故在。而且柴桑幽士。其词澹然以平。燕狱羁囚。其文肆然以豪。斯其世何世也。岂天地间正气中声。初未尝尧存桀亡。而乃与夫不死之人心。交贯互宣。为雅乐为粹词。而不容已耶。然则恶在政也。亦视其人之何如耳。钱虞山有学集出于 明后。余观其诗若文。大都气轻而促。言戚而厖。哀之固也。何其泥也耶。尝考 皇朝遗史。虞山其人。虽以东林之淑类称。而所性儇躁。矜其小慧。闇于大道。于其阁讼。可见侏儒之一节矣。而况尝位大臣之列。而不能一死于国破君亡之馀。落发披条。窜身丛林。此其心之先身而死久矣。是安得不易乎世而卓然自立者耶。故其文澜才燄。虽王长当世。自以高出 本朝。远绍唐,宋。而卒与夫水调八破之流。烂熳同归也无怪矣。呜呼。彼固不祥之人。而词又不祥之音也。谓宜斥以远之。惟恐或似而顾今之人。方且赏爱之拟议之。惟恐其不能似也。抑又何也。岂其文澜才焰。能使人易眩耶。将时变所渐。有不约而同者存耶。呜呼殆矣。书韩山李公一源哭亡婿文后
悔窝集卷四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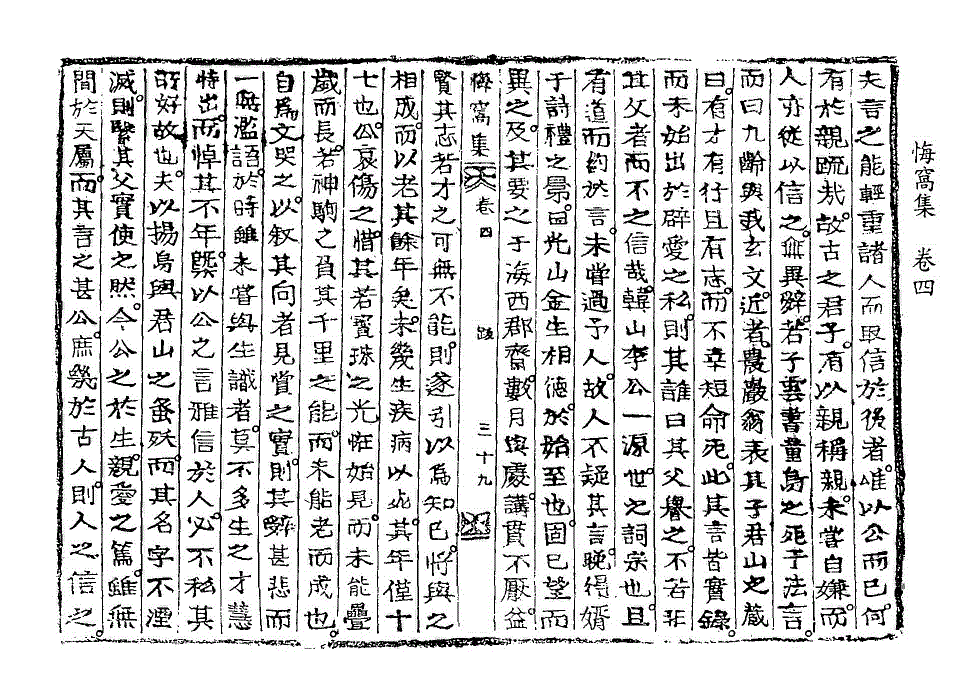 夫言之能轻重诸人而取信于后者。唯以公而已。何有于亲疏哉。故古之君子。有以亲称亲。未尝自嫌。而人亦从以信之。无异辞。若子云书童乌之死于法言。而曰九龄与我玄文。近者。农岩翁表其子君山之藏曰。有才有行且有志。而不幸短命死。此其言皆实录。而未始出于辟爱之私。则其谁曰其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而不之信哉。韩山李公一源。世之词宗也。且有道而约于言。未尝过予人。故人不疑其言。晚得婿于诗礼之昆。曰光山金生相德。于始至也。固已望而异之。及其要之于海西郡斋。数月与处。讲贯不厌。益贤其志若才之可无不能。则遂引以为知己。将与之相成。而以老其馀年矣。未几生疾病以死。其年仅十七也。公哀伤之。惜其若宝珠之光怪始见。而未能叠岁而长。若神驹之负其千里之能。而未能老而成也。自为文哭之。以叙其向者见赏之实。则其辞甚悲而一无滥语。于时虽未尝与生识者。莫不多生之才慧特出。而悼其不年。槩以公之言雅信于人。必不私其所好故也。夫以扬乌与君山之蚤夭。而其名字不湮灭。则繄其父实使之然。今公之于生。亲爱之笃。虽无间于天属。而其言之甚公。庶几于古人。则人之信之。
夫言之能轻重诸人而取信于后者。唯以公而已。何有于亲疏哉。故古之君子。有以亲称亲。未尝自嫌。而人亦从以信之。无异辞。若子云书童乌之死于法言。而曰九龄与我玄文。近者。农岩翁表其子君山之藏曰。有才有行且有志。而不幸短命死。此其言皆实录。而未始出于辟爱之私。则其谁曰其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而不之信哉。韩山李公一源。世之词宗也。且有道而约于言。未尝过予人。故人不疑其言。晚得婿于诗礼之昆。曰光山金生相德。于始至也。固已望而异之。及其要之于海西郡斋。数月与处。讲贯不厌。益贤其志若才之可无不能。则遂引以为知己。将与之相成。而以老其馀年矣。未几生疾病以死。其年仅十七也。公哀伤之。惜其若宝珠之光怪始见。而未能叠岁而长。若神驹之负其千里之能。而未能老而成也。自为文哭之。以叙其向者见赏之实。则其辞甚悲而一无滥语。于时虽未尝与生识者。莫不多生之才慧特出。而悼其不年。槩以公之言雅信于人。必不私其所好故也。夫以扬乌与君山之蚤夭。而其名字不湮灭。则繄其父实使之然。今公之于生。亲爱之笃。虽无间于天属。而其言之甚公。庶几于古人。则人之信之。悔窝集卷四 第 336L 页
 不亦宜乎。而且当世之相信如此。其见信于来后。又从可知也。呜呼。生其不朽矣。虽然。公则不知其言之足以存生于久载。而必求他人之有以张之。能者之叙述既备矣。而犹辱及于不佞。岂公恐后人之或不吾信。而谓疏者之言。特公于亲者之自为也耶。则不已过乎。然公既勤于见属。则义不可以不能辞也。遂略书于公文之后。使后之人。益信其言一出于公。视古君子无愧云。
不亦宜乎。而且当世之相信如此。其见信于来后。又从可知也。呜呼。生其不朽矣。虽然。公则不知其言之足以存生于久载。而必求他人之有以张之。能者之叙述既备矣。而犹辱及于不佞。岂公恐后人之或不吾信。而谓疏者之言。特公于亲者之自为也耶。则不已过乎。然公既勤于见属。则义不可以不能辞也。遂略书于公文之后。使后之人。益信其言一出于公。视古君子无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