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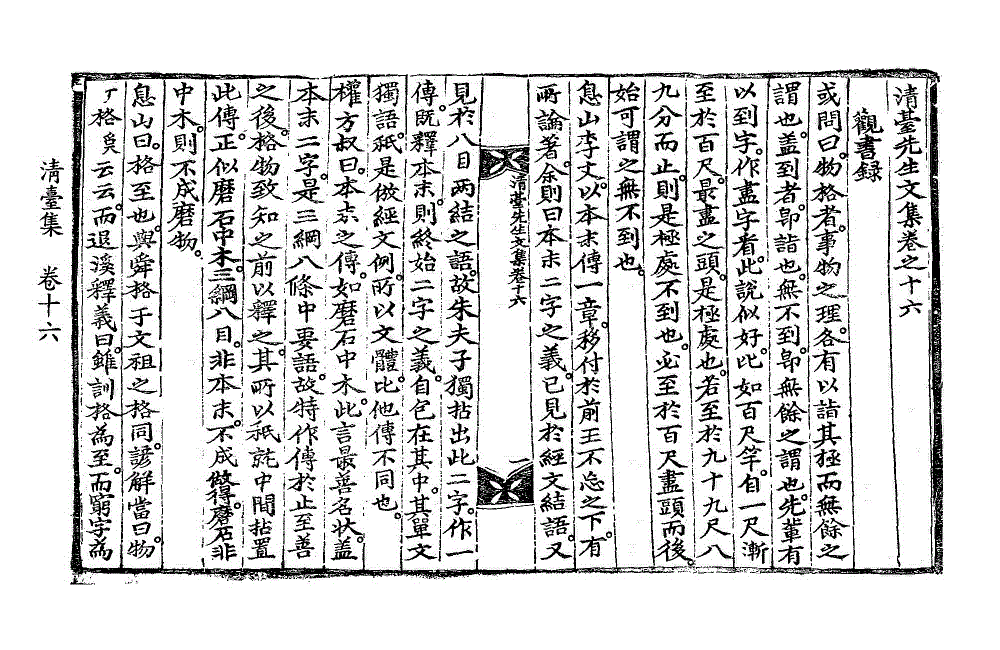 观书录
观书录或问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之谓也。盖到者。即诣也。无不到。即无馀之谓也。先辈有以到字。作尽字看。此说似好。比如百尺竿。自一尺渐至于百尺。最尽之头。是极处也。若至于九十九尺八九分而止。则是极处不到也。必至于百尺尽头而后。始可谓之无不到也。
息山李丈。以本末传一章。移付于前王不忘之下。有所论著。余则曰本末二字之义。已见于经文结语。又见于八目两结之语。故朱夫子独拈出此二字。作一传。既释本末。则终始二字之义。自包在其中。其单文独语。秖是仿经文例。所以文体。比他传不同也。
权方叔曰。本末之传。如磨石中木。此言最善名状。盖本末二字。是三纲八条中要语。故特作传于止至善之后。格物致知之前以释之。其所以秖就中间拈置此传。正似磨石中木。三纲八目。非本末。不成做得。磨石非中木。则不成磨物。
息山曰。格至也。与舜格于文祖之格同。谚解当曰。物()格(𨵚)云云。而退溪释义曰。虽训格为至。而穷字为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5L 页
 重。当曰物()格(𨵚)云云。细看补亡章。则有曰。即物而穷其理。又曰。惟于理。有未穷。又曰。因其所知之理而益穷之。盖以穷字为重也。退溪训释。十分亭当。不可移易。
重。当曰物()格(𨵚)云云。细看补亡章。则有曰。即物而穷其理。又曰。惟于理。有未穷。又曰。因其所知之理而益穷之。盖以穷字为重也。退溪训释。十分亭当。不可移易。小人閒居一章。说出小人情状之隐秘处。毫发无遗。语似迫切。而有欠于圣贤宽容和平气像。然诚意工夫。极细极密。故于恶恶处。不得不如此说。
李大游以大学不倍于上。为民不背叛于其上。密庵答渠书曰。孤者。是自家孤幼。不倍者。民不背上之所为。而各自恤其孤幼也。详见本注。则密翁说甚好。盖非他人之孤而乃自家亲戚中孤幼也。如孟子所谓幼吾幼而改幼言孤者。孤是无依。尤合矜恤。是故。民有所兴感而不背上之所为也。
大学多错简。有亡章。故朱子一生精力。尽在此书。编错补亡。极尽无欠。观易箦前三日。改定诚意集注一款。可知也。后人议论似不敢到。而王鲁斋及蕫方诸儒。别生他论。我东晦斋先生。以物有本末。知止有定两节。移作格致传。以代补亡。且听讼一章。移作经文结语。退溪答李仲久书。详论此事。以为不可。此实千古确论。而晦斋庶孙李浚上稣斋书曰。退溪先生晚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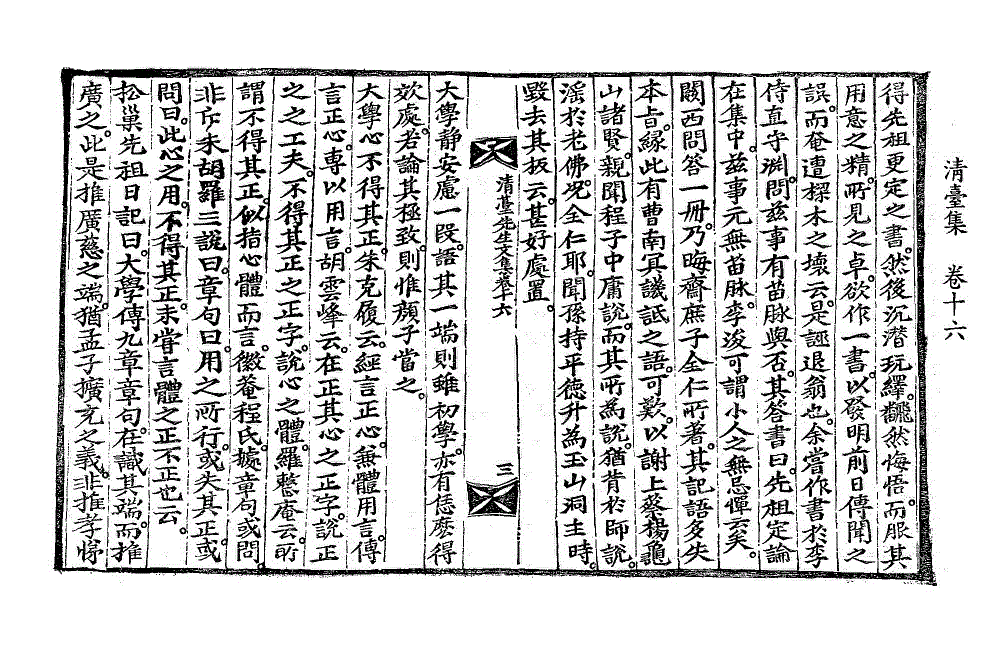 得先祖更定之书。然后沉潜玩绎。翻然悔悟。而服其用意之精。所见之卓。欲作一书。以发明前日传闻之误。而奄遭梁木之坏云。是诬退翁也。余尝作书于李侍直守渊。问玆事有苗脉与否。其答书曰。先祖定论在集中。玆事元无苗脉。李浚可谓小人之无忌惮云矣。
得先祖更定之书。然后沉潜玩绎。翻然悔悟。而服其用意之精。所见之卓。欲作一书。以发明前日传闻之误。而奄遭梁木之坏云。是诬退翁也。余尝作书于李侍直守渊。问玆事有苗脉与否。其答书曰。先祖定论在集中。玆事元无苗脉。李浚可谓小人之无忌惮云矣。关西问答一册。乃晦斋庶子全仁所著。其记语多失本旨。缘此有曹南冥讥诋之语。可叹。以谢上蔡,杨龟山诸贤。亲闻程子中庸说。而其所为说。犹背于师说。淫于老佛。况全仁耶。闻孙持平德升为玉山洞主时。毁去其板云。甚好处置。
大学静安虑一段。语其一端则虽初学。亦有恁么得效处。若论其极致。则惟颜子当之。
大学心不得其正。朱克履云。经言正心。兼体用言。传言正心。专以用言。胡云峰云。在正其心之正字。说正之之工夫。不得其正之正字。说心之体。罗整庵云。所谓不得其正。似指心体而言。徽庵程氏。据章句或问。非斥朱胡罗三说曰。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问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尝言体之正不正也云。
松巢先祖日记曰。大学传九章章句。在识其端。而推广之。此是推广慈之端。犹孟子扩充之义。非推孝悌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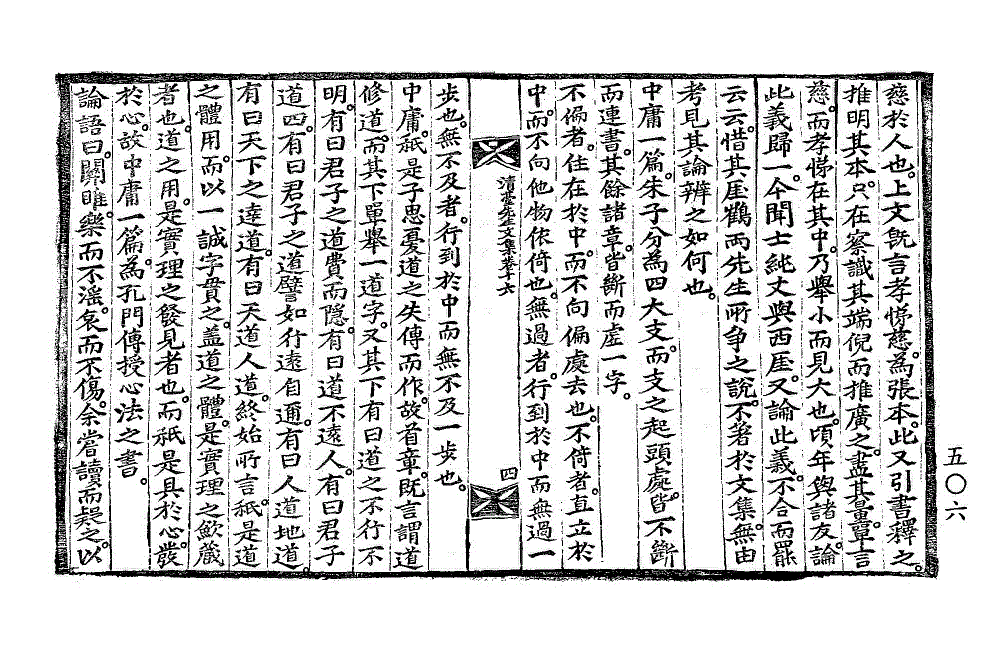 慈于人也。上文既言孝悌慈。为张本。此又引书释之。推明其本。只在察识其端倪而推广之。尽其量。单言慈。而孝悌在其中。乃举小而见大也。顷年与诸友。论此义归一。今闻士纯丈与西厓。又论此义。不合而罢云云。惜其厓鹤两先生所争之说。不著于文集。无由考见其论辨之如何也。
慈于人也。上文既言孝悌慈。为张本。此又引书释之。推明其本。只在察识其端倪而推广之。尽其量。单言慈。而孝悌在其中。乃举小而见大也。顷年与诸友。论此义归一。今闻士纯丈与西厓。又论此义。不合而罢云云。惜其厓鹤两先生所争之说。不著于文集。无由考见其论辨之如何也。中庸一篇。朱子分为四大支。而支之起头处。皆不断而连书。其馀诸章。皆断而虚一字。
不偏者。住在于中。而不向偏处去也。不倚者。直立于中。而不向他物依倚也。无过者。行到于中而无过一步也。无不及者。行到于中而无不及一步也。
中庸。秖是子思忧道之失传而作。故首章。既言谓道修道。而其下单举一道字。又其下有曰道之不行不明。有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有曰道不远人。有曰君子道四。有曰君子之道譬如行远自迩。有曰人道地道。有曰天下之达道。有曰天道人道。终始所言。秖是道之体用。而以一诚字贯之。盖道之体。是实理之敛藏者也。道之用。是实理之发见者也。而秖是具于心。发于心。故中庸一篇。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
论语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余尝读而疑之。以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7H 页
 为关雎之展转反侧。是忧也。非哀也。更思之。诗是性情之发。故夫子就七情上。拈哀乐二字说。而哀字与忧字同。是以集注曰。有展转反侧之忧。且忧者。属于哀。古人以居丧为宅忧忧中及自罹忧苦等语。与哀字义通。
为关雎之展转反侧。是忧也。非哀也。更思之。诗是性情之发。故夫子就七情上。拈哀乐二字说。而哀字与忧字同。是以集注曰。有展转反侧之忧。且忧者。属于哀。古人以居丧为宅忧忧中及自罹忧苦等语。与哀字义通。张横渠曰。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既曰夫子之言。则是居常语之矣。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因有是说云。而详考本文。则朱子注说。以夫子不常语之故。子贡不得以听闻也。与横渠说。大不同。就两说玩味。则朱子说。是正义。
孟子好辩章集注。程子曰。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近思录辨异端条。明道先生曰。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两说皆出于程子。而二书所录。互相不同可疑。朱子答汪尚书书曰。杨朱学为义者也。而偏于为我。墨翟学为仁者也。而偏于兼爱。本其设心。岂有邪哉。庆源辅氏曰。杨氏以为我为义。而非圣人所谓义。墨氏以兼爱为仁。而非圣人所谓仁。所以为异端。(止此)集诸家说而观之。则杨朱为义。墨翟为仁之说。似是。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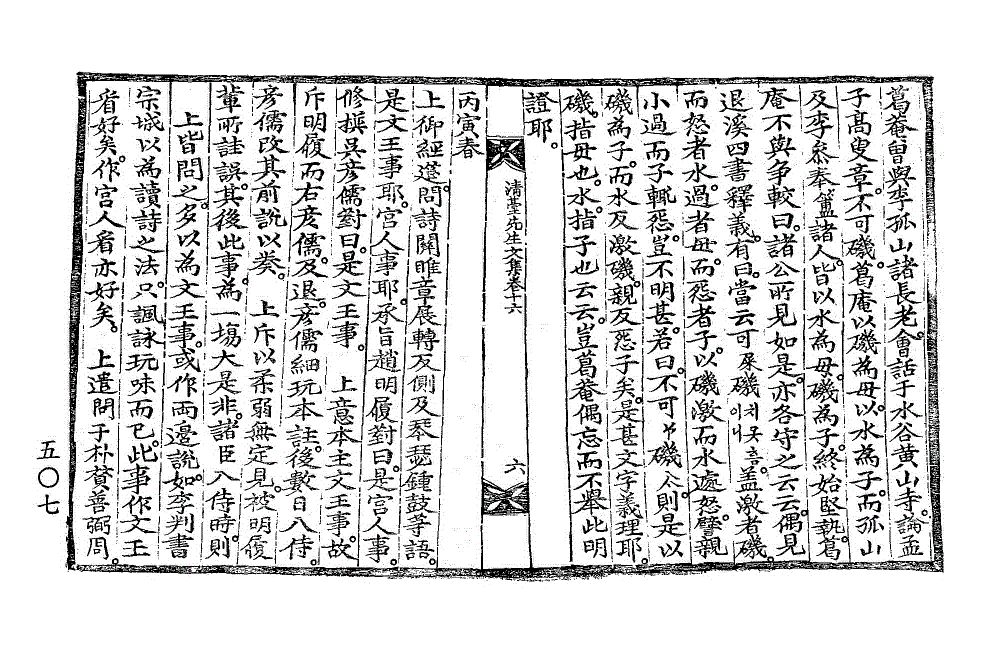 葛庵曾与李孤山诸长老。会话于水谷黄山寺。论孟子高叟章。不可矶。葛庵以矶为母。以水为子。而孤山及李参奉(簠)诸人。皆以水为母。矶为子。终始坚执。葛庵不与争较曰。诸公所见如是。亦各守之云云。偶见退溪四书释义。有曰。当云可()矶(치못흠이니)。盖激者矶。而怒者水。过者母。而怨者子。以矶激而水遽怒。譬亲小过而子辄怨。岂不明甚。若曰。不可(𥳄)矶(𣼩)。则是以矶为子。而水反激矶。亲反怨子矣。是甚文字义理耶。矶。指母也。水。指子也云云。岂葛庵偶忘而不举此明證耶。
葛庵曾与李孤山诸长老。会话于水谷黄山寺。论孟子高叟章。不可矶。葛庵以矶为母。以水为子。而孤山及李参奉(簠)诸人。皆以水为母。矶为子。终始坚执。葛庵不与争较曰。诸公所见如是。亦各守之云云。偶见退溪四书释义。有曰。当云可()矶(치못흠이니)。盖激者矶。而怒者水。过者母。而怨者子。以矶激而水遽怒。譬亲小过而子辄怨。岂不明甚。若曰。不可(𥳄)矶(𣼩)。则是以矶为子。而水反激矶。亲反怨子矣。是甚文字义理耶。矶。指母也。水。指子也云云。岂葛庵偶忘而不举此明證耶。丙寅春 上御经筵。问诗关雎章展转反侧及琴瑟钟鼓等语。是文王事耶。宫人事耶。承旨赵明履对曰。是宫人事。修撰吴彦儒对曰。是文王事。 上意本主文王事。故斥明履而右彦儒。及退。彦儒细玩本注。后数日入侍。彦儒改其前说以奏。 上斥以柔弱无定见。被明履辈所诖误。其后此事。为一场大是非。诸臣入侍时。则 上皆问之。多以为文王事。或作两边说。如李判书宗城以为读诗之法。只讽咏玩味而已。此事作文王看好矣。作宫人看亦好矣。 上遣问于朴赞善弼周。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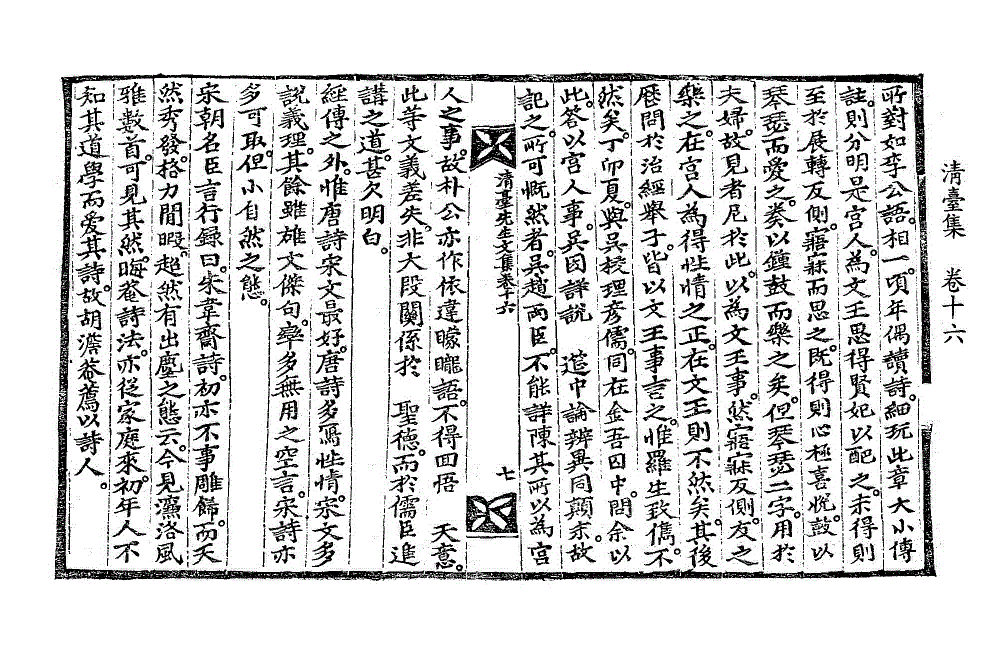 所对如李公语。相一。顷年偶读诗。细玩此章大小传注。则分明是宫人。为文王思得贤妃以配之。未得则至于展转反侧。寤寐而思之。既得则心极喜悦。鼓以琴瑟而爱之。奏以钟鼓而乐之矣。但琴瑟二字。用于夫妇。故见者尼于此。以为文王事。然寤寐反侧。友之乐之。在宫人为得性情之正。在文王则不然矣。其后历问于治经举子。皆以文王事言之。惟罗生致俊。不然矣。丁卯夏。与吴校理彦儒。同在金吾囚中。问余以此。答以宫人事。吴因详说 筵中论辨异同颠末。故记之。所可慨然者。吴,赵两臣。不能详陈其所以为宫人之事。故朴公亦作依违矇眬语。不得回悟 天意。此等文义差失。非大段关系于 圣德。而于儒臣进讲之道。甚欠明白。
所对如李公语。相一。顷年偶读诗。细玩此章大小传注。则分明是宫人。为文王思得贤妃以配之。未得则至于展转反侧。寤寐而思之。既得则心极喜悦。鼓以琴瑟而爱之。奏以钟鼓而乐之矣。但琴瑟二字。用于夫妇。故见者尼于此。以为文王事。然寤寐反侧。友之乐之。在宫人为得性情之正。在文王则不然矣。其后历问于治经举子。皆以文王事言之。惟罗生致俊。不然矣。丁卯夏。与吴校理彦儒。同在金吾囚中。问余以此。答以宫人事。吴因详说 筵中论辨异同颠末。故记之。所可慨然者。吴,赵两臣。不能详陈其所以为宫人之事。故朴公亦作依违矇眬语。不得回悟 天意。此等文义差失。非大段关系于 圣德。而于儒臣进讲之道。甚欠明白。经传之外。惟唐诗宋文最好。唐诗多写性情。宋文多说义理。其馀虽雄文杰句。率多无用之空言。宋诗亦多可取。但小自然之态。
宋朝名臣言行录曰。朱韦斋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閒暇。超然有出尘之态云。今见濂洛风雅数首。可见其然。晦庵诗法。亦从家庭来。初年人不知其道学而爱其诗。故胡澹庵荐以诗人。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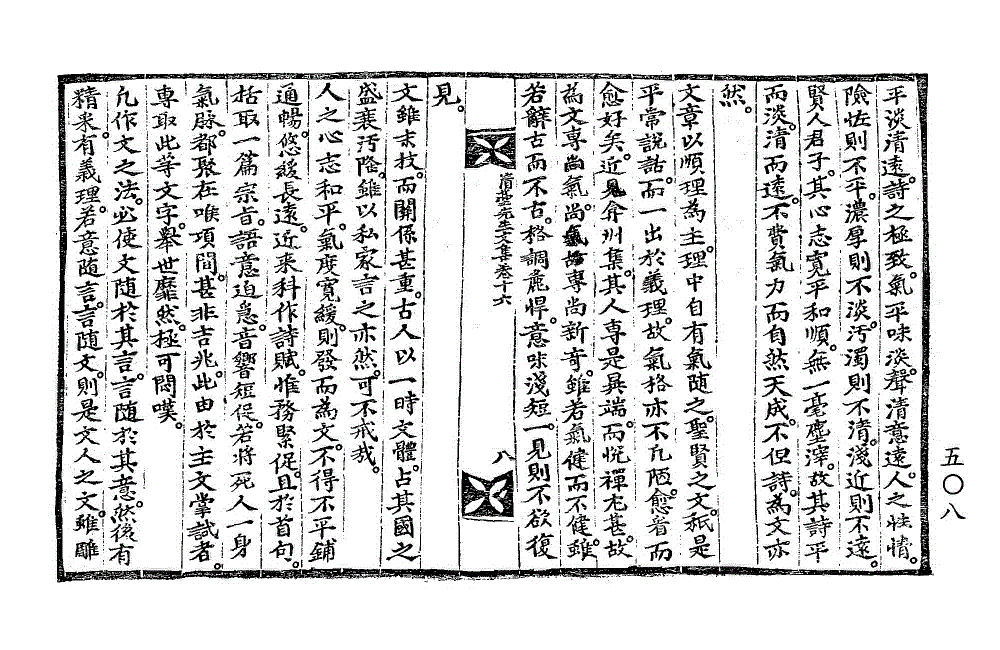 平淡清远。诗之极致。气平味淡。声清意远。人之性情。险怪则不平。浓厚则不淡。污浊则不清。浅近则不远。贤人君子。其心志宽平和顺。无一毫尘滓。故其诗平而淡。清而远。不费气力而自然天成。不但诗。为文亦然。
平淡清远。诗之极致。气平味淡。声清意远。人之性情。险怪则不平。浓厚则不淡。污浊则不清。浅近则不远。贤人君子。其心志宽平和顺。无一毫尘滓。故其诗平而淡。清而远。不费气力而自然天成。不但诗。为文亦然。文章以顺理为主。理中自有气随之。圣贤之文。秖是平常说话。而一出于义理。故气格亦不凡陋。愈看而愈好矣。近见弇州集。其人专是异端。而悦禅尤甚。故为文专尚气。尚气故专尚新奇。虽若气健而不健。虽若辞古而不古。格调粗悍。意味浅短。一见则不欲复见。
文虽末技。而关系甚重。古人以一时文体。占其国之盛衰污隆。虽以私家言之亦然。可不戒哉。
人之心志和平。气度宽缓。则发而为文。不得不平铺通畅。悠缓长远。近来科作诗赋。惟务紧促。且于首句。括取一篇宗旨。语意迫急。音响短促。若将死人一身气脉。都聚在喉项间。甚非吉兆。此由于主文掌试者。专取此等文字。举世靡然。极可闷叹。
凡作文之法。必使文随于其言。言随于其意。然后有精采。有义理。若意随言。言随文。则是文人之文。虽雕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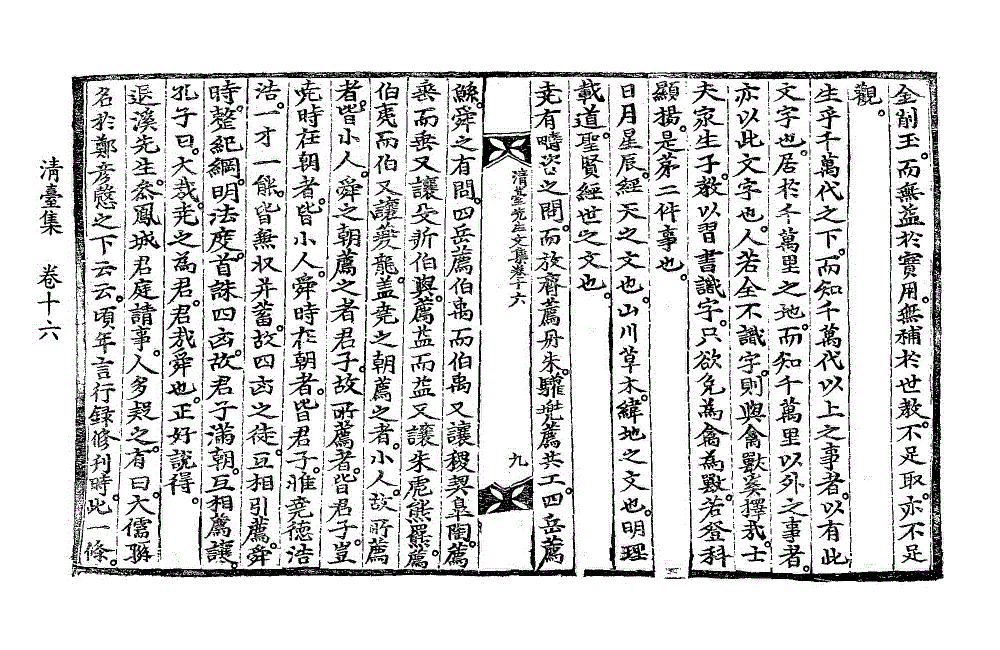 金削玉。而无益于实用。无补于世教。不足取。亦不足观。
金削玉。而无益于实用。无补于世教。不足取。亦不足观。生乎千万代之下。而知千万代以上之事者。以有此文字也。居于千万里之地。而知千万里以外之事者。亦以此文字也。人若全不识字。则与禽兽奚择哉。士夫家生子。教以习书识字。只欲免为禽为兽。若登科显扬。是第二件事也。
日月星辰。经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纬地之文也。明理载道。圣贤经世之文也。
尧有畴咨之问。而放齐荐丹朱。驩兜荐共工。四岳荐鲧。舜之有问。四岳荐伯禹而伯禹又让稷契皋陶。荐垂而垂又让殳斨伯与。荐益而益又让朱虎熊罴。荐伯夷而伯又让夔龙。盖尧之朝荐之者。小人。故所荐者。皆小人。舜之朝荐之者君子。故所荐者。皆君子。岂尧时在朝者。皆小人。舜时在朝者。皆君子。惟尧德浩浩。一才一能。皆兼收并蓄。故四凶之徒。互相引荐。舜时。整纪纲。明法度。首诛四凶。故君子满朝。互相荐让。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正好说得。
退溪先生。参凤城君庭请事。人多疑之。有曰。大儒联名于郑彦悫之下云云。顷年言行录修刊时。此一条。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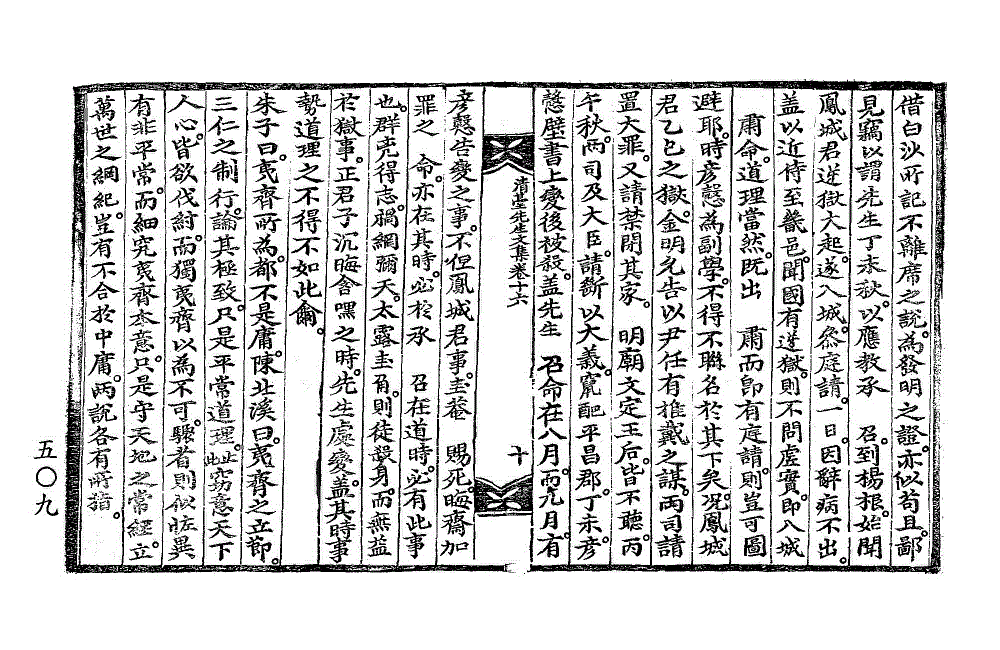 借白沙所记不离席之说。为发明之證。亦似苟且。鄙见窃以谓先生丁未秋。以应教承 召。到杨根。始闻凤城君逆狱大起。遂入城。参庭请。一日。因辞病不出。盖以近侍至畿邑。闻国有逆狱。则不问虚实。即入城 肃命。道理当然。既出 肃而即有庭请。则岂可图避耶。时彦悫为副学。不得不联名于其下矣。况凤城君乙巳之狱。金明允告以尹任有推戴之谋。两司请置大罪。又请禁闭其家。 明庙文定王后。皆不听。丙午秋。两司及大臣。请断以大义。窜配平昌郡。丁未。彦悫壁书上变后被杀。盖先生 召命在八月。而九月。有彦悫告变之事。不但凤城君事。圭庵 赐死。晦斋加罪之 命。亦在其时。必于承 召在道时。必有此事也。群凶得志。祸网弥天。太露圭角。则徒杀身。而无益于狱事。正君子沉晦含嘿之时。先生处变。盖其时事势道理之不得不如此尔。
借白沙所记不离席之说。为发明之證。亦似苟且。鄙见窃以谓先生丁未秋。以应教承 召。到杨根。始闻凤城君逆狱大起。遂入城。参庭请。一日。因辞病不出。盖以近侍至畿邑。闻国有逆狱。则不问虚实。即入城 肃命。道理当然。既出 肃而即有庭请。则岂可图避耶。时彦悫为副学。不得不联名于其下矣。况凤城君乙巳之狱。金明允告以尹任有推戴之谋。两司请置大罪。又请禁闭其家。 明庙文定王后。皆不听。丙午秋。两司及大臣。请断以大义。窜配平昌郡。丁未。彦悫壁书上变后被杀。盖先生 召命在八月。而九月。有彦悫告变之事。不但凤城君事。圭庵 赐死。晦斋加罪之 命。亦在其时。必于承 召在道时。必有此事也。群凶得志。祸网弥天。太露圭角。则徒杀身。而无益于狱事。正君子沉晦含嘿之时。先生处变。盖其时事势道理之不得不如此尔。朱子曰。夷齐所为。都不是庸。陈北溪曰。夷齐之立节。三仁之制行。论其极致。只是平常道理。(止此)窃意天下人心。皆欲伐纣。而独夷齐以为不可。骤看则似怪异有非平常。而细究夷齐本意。只是守天地之常经。立万世之纲纪。岂有不合于中庸。两说各有所指。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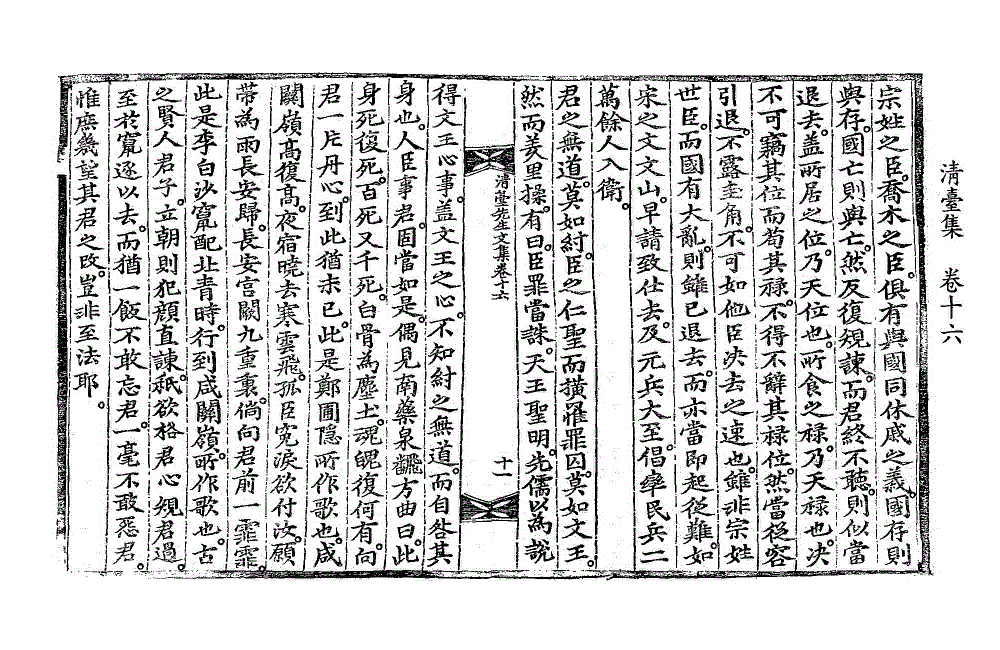 宗姓之臣。乔木之臣。俱有与国同休戚之义。国存则与存。国亡则与亡。然反复规谏。而君终不听。则似当退去。盖所居之位。乃天位也。所食之禄。乃天禄也。决不可窃其位而苟其禄。不得不辞其禄位。然当从容引退。不露圭角。不可如他臣决去之速也。虽非宗姓世臣。而国有大乱。则虽已退去。而亦当即起从难。如宋之文文山。早请致仕去。及元兵大至。倡率民兵二万馀人入卫。
宗姓之臣。乔木之臣。俱有与国同休戚之义。国存则与存。国亡则与亡。然反复规谏。而君终不听。则似当退去。盖所居之位。乃天位也。所食之禄。乃天禄也。决不可窃其位而苟其禄。不得不辞其禄位。然当从容引退。不露圭角。不可如他臣决去之速也。虽非宗姓世臣。而国有大乱。则虽已退去。而亦当即起从难。如宋之文文山。早请致仕去。及元兵大至。倡率民兵二万馀人入卫。君之无道。莫如纣。臣之仁圣而横罹罪囚。莫如文王。然而羑里操。有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先儒以为说得文王心事。盖文王之心。不知纣之无道。而自咎其身也。人臣事君。固当如是。偶见南药泉翻方曲曰。此身死复死。百死又千死。白骨为尘土。魂魄复何有。向君一片丹心。到此犹未已。此是郑圃隐所作歌也。咸关岭高复高。夜宿晓去寒云飞。孤臣冤泪欲付汝。愿带为雨长安归。长安宫阙九重里。倘向君前一霏霏。此是李白沙窜配北青时。行到咸关岭。所作歌也。古之贤人君子。立朝则犯颜直谏。秖欲格君心规君过。至于窜逐以去。而犹一饭不敢忘君。一毫不敢怨君。惟庶几望其君之改。岂非至法耶。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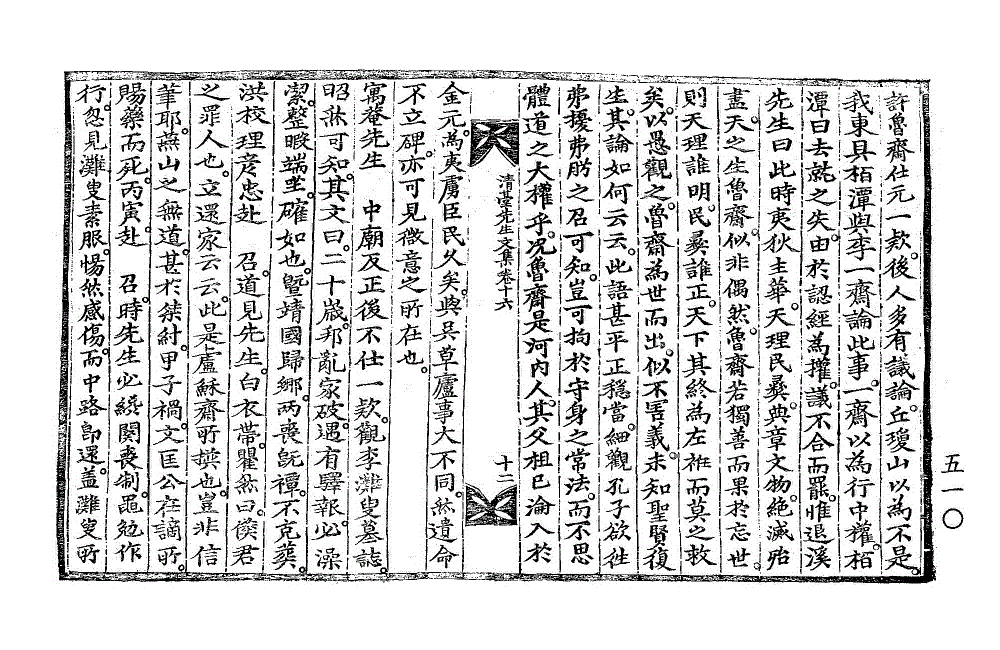 许鲁斋仕元一款。后人多有议论。丘琼山以为不是。我东具柏潭与李一斋论此事。一斋以为行中权。柏潭曰去就之失。由于认经为权。议不合而罢。惟退溪先生曰此时夷狄主华。天理民彝。典章文物。绝灭殆尽。天之生鲁斋。似非偶然。鲁斋若独善而果于忘世。则天理谁明。民彝谁正。天下其终为左衽而莫之救矣。以愚观之。鲁斋为世而出。似不害义。未知圣贤复生。其论如何云云。此语甚平正稳当。细观孔子欲往弗扰弗肸之召可知。岂可拘于守身之常法。而不思体道之大权乎。况鲁斋是河内人。其父祖已沦入于金元。为夷虏臣民久矣。与吴草庐事大不同。然遗命不立碑。亦可见微意之所在也。
许鲁斋仕元一款。后人多有议论。丘琼山以为不是。我东具柏潭与李一斋论此事。一斋以为行中权。柏潭曰去就之失。由于认经为权。议不合而罢。惟退溪先生曰此时夷狄主华。天理民彝。典章文物。绝灭殆尽。天之生鲁斋。似非偶然。鲁斋若独善而果于忘世。则天理谁明。民彝谁正。天下其终为左衽而莫之救矣。以愚观之。鲁斋为世而出。似不害义。未知圣贤复生。其论如何云云。此语甚平正稳当。细观孔子欲往弗扰弗肸之召可知。岂可拘于守身之常法。而不思体道之大权乎。况鲁斋是河内人。其父祖已沦入于金元。为夷虏臣民久矣。与吴草庐事大不同。然遗命不立碑。亦可见微意之所在也。寓庵先生 中庙反正后不仕一款。观李滩叟墓志。昭然可知。其文曰。二十岁。邦乱家破。遇有驿报。必澡洁。整暇端坐。确如也。暨靖国归乡。两丧既禫。不克葬。洪校理彦忠赴 召。道见先生。白衣带。瞿然曰。仆君之罪人也。立还家云云。此是卢稣斋所撰也。岂非信笔耶。燕山之无道。甚于桀纣。甲子祸。文匡公在谪所。赐药而死。丙寅。赴 召。时先生必才阕丧制。黾勉作行。忽见滩叟素服。惕然感伤。而中路即还。盖滩叟所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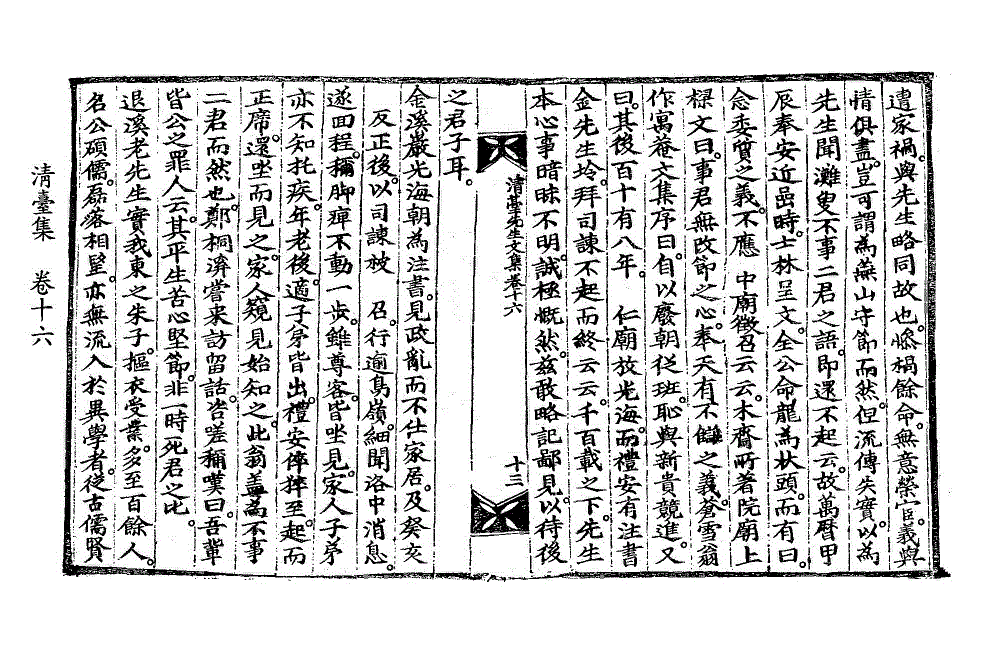 遭家祸。与先生略同故也。惨祸馀命。无意荣宦。义与情俱尽。岂可谓为燕山守节而然。但流传失实。以为先生闻滩叟不事二君之语。即还不起云。故万历甲辰奉安近岩时。士林呈文。全公命龙为状头。而有曰。念委质之义。不应 中庙徵召云云。木斋所著院庙上梁文曰。事君无改节之心。奉天有不雠之义。苍雪翁作寓庵文集序曰。自以废朝从班。耻与新贵竞进。又曰。其后百十有八年。 仁庙放光海。而礼安有注书金先生坽。拜司谏不起而终云云。千百载之下。先生本心事暗昧不明。诚极慨然。玆敢略记鄙见。以待后之君子耳。
遭家祸。与先生略同故也。惨祸馀命。无意荣宦。义与情俱尽。岂可谓为燕山守节而然。但流传失实。以为先生闻滩叟不事二君之语。即还不起云。故万历甲辰奉安近岩时。士林呈文。全公命龙为状头。而有曰。念委质之义。不应 中庙徵召云云。木斋所著院庙上梁文曰。事君无改节之心。奉天有不雠之义。苍雪翁作寓庵文集序曰。自以废朝从班。耻与新贵竞进。又曰。其后百十有八年。 仁庙放光海。而礼安有注书金先生坽。拜司谏不起而终云云。千百载之下。先生本心事暗昧不明。诚极慨然。玆敢略记鄙见。以待后之君子耳。金溪岩光海朝为注书。见政乱而不仕家居。及癸亥 反正后。以司谏被 召。行逾鸟岭。细闻洛中消息。遂回程。称脚痹不动一步。虽尊客。皆坐见。家人子弟亦不知托疾。年老后。适子弟皆出。礼安倅猝至。起而正席。还坐而见之。家人窥见始知之。此翁盖为不事二君而然也。郑桐溪尝来访留话。咨嗟称叹曰。吾辈皆公之罪人云。其平生苦心坚节。非一时死君之比。
退溪老先生实我东之朱子。抠衣受业。多至百馀人。名公硕儒。磊落相望。亦无流入于异学者。从古儒贤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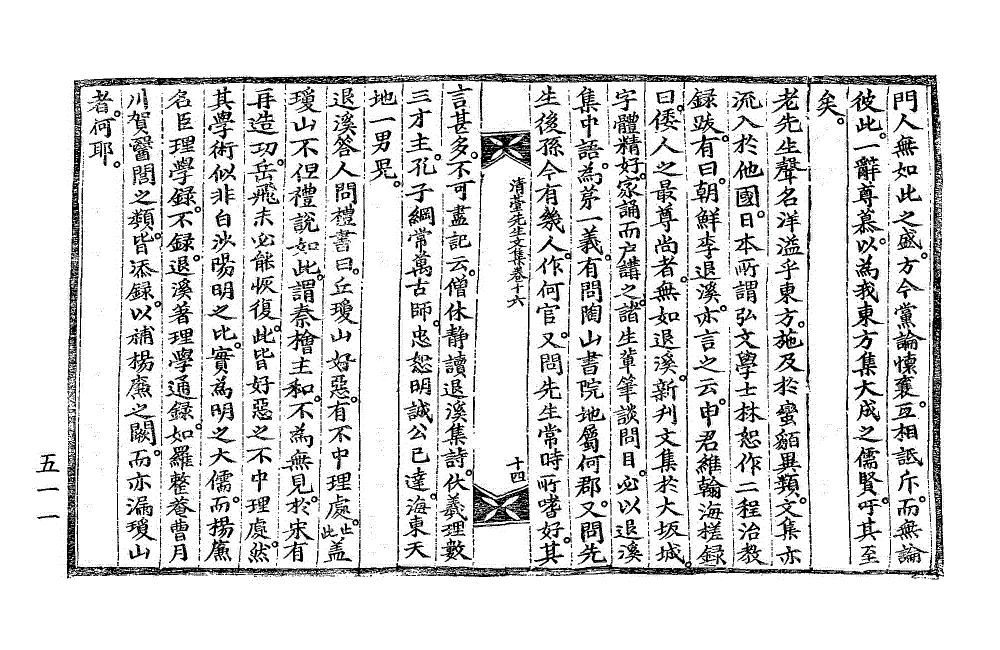 门人无如此之盛。方今党论怀襄。互相诋斥。而无论彼此。一辞尊慕。以为我东方集大成之儒贤。吁其至矣。
门人无如此之盛。方今党论怀襄。互相诋斥。而无论彼此。一辞尊慕。以为我东方集大成之儒贤。吁其至矣。老先生声名洋溢乎东方。施及于蛮貊异类。文集亦流入于他国。日本所谓弘文学士林恕作二程治教录跋。有曰。朝鲜李退溪。亦言之云。申君维翰海槎录曰。倭人之最尊尚者。无如退溪。新刊文集于大坂城。字体精好。家诵而户讲之。诸生辈笔谈问目。必以退溪集中语。为第一义。有问陶山书院地属何郡。又问先生后孙今有几人。作何官。又问先生常时所嗜好。其言甚多。不可尽记云。僧休静读退溪集诗。伏羲理数三才主。孔子纲常万古师。忠恕明诚公已达。海东天地一男儿。
退溪答人问礼书曰。丘琼山好恶。有不中理处。(止此)盖琼山不但礼说如此。谓秦桧主和。不为无见。于宋有再造功。岳飞未必能恢复。此皆好恶之不中理处。然其学术似非白沙阳明之比。实为明之大儒。而杨廉名臣理学录。不录。退溪著理学通录。如罗整庵曹月川贺医闾之类。皆添录。以补杨廉之阙。而亦漏琼山者。何耶。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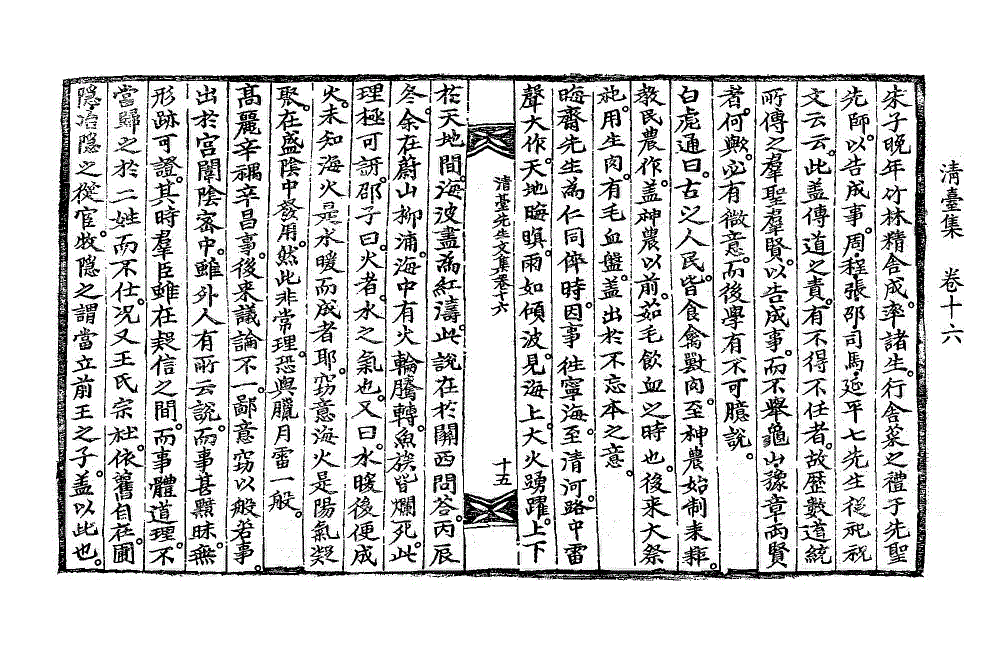 朱子晚年竹林精舍成。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告成事。周,程,张,邵,司马,延平七先生从祀祝文云云。此盖传道之责。有不得不任者。故历数道统所传之群圣群贤。以告成事。而不举龟山,豫章两贤者。何欤。必有微意。而后学有不可臆说。
朱子晚年竹林精舍成。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告成事。周,程,张,邵,司马,延平七先生从祀祝文云云。此盖传道之责。有不得不任者。故历数道统所传之群圣群贤。以告成事。而不举龟山,豫章两贤者。何欤。必有微意。而后学有不可臆说。白虎通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神农始制耒耟。教民农作。盖神农以前。茹毛饮血之时也。后来大祭祀。用生肉。有毛血盘。盖出于不忘本之意。
晦斋先生为仁同倅时。因事往宁海。至清河。路中雷声大作。天地晦暝。雨如倾波。见海上。大火踊跃。上下于天地间。海波尽为红涛。此说在于关西问答。丙辰冬。余在蔚山柳浦。海中有火轮腾转。鱼族皆烂死。此理极可讶。邵子曰。火者。水之气也。又曰。水暖后便成火。未知海火是水暖而成者耶。窃意海火是阳气凝聚。在盛阴中发用。然此非常理。恐与腊月雷一般。
高丽辛祦辛昌事。后来议论不一。鄙意窃以般若事。出于宫闱阴密中。虽外人有所云说。而事甚黯昧。无形迹可證。其时群臣虽在疑信之间。而事体道理。不当归之于二姓而不仕。况又王氏宗社。依旧自在。圃隐,冶隐之从宦。牧隐之谓当立前王之子。盖以此也。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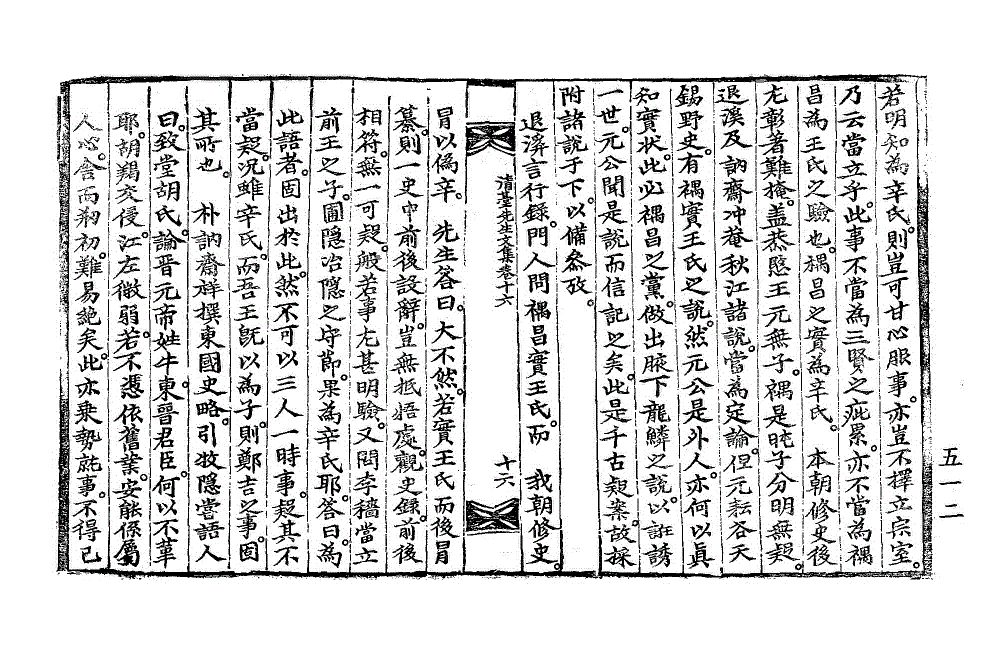 若明知为辛氏。则岂可甘心服事。亦岂不择立宗室。乃云当立乎。此事不当为三贤之疵累。亦不当为祦昌为王氏之验也。祦昌之实为辛氏。 本朝修史后尤彰著难掩。盖恭悯王元无子。祦是旽子分明无疑。退溪及讷斋冲庵秋江诸说。当为定论。但元耘谷天锡野史。有祦实王氏之说。然元公是外人。亦何以真知实状。此必祦昌之党。做出腋下龙鳞之说。以诳诱一世。元公闻是说而信记之矣。此是千古疑案。故采附诸说于下。以备参考。
若明知为辛氏。则岂可甘心服事。亦岂不择立宗室。乃云当立乎。此事不当为三贤之疵累。亦不当为祦昌为王氏之验也。祦昌之实为辛氏。 本朝修史后尤彰著难掩。盖恭悯王元无子。祦是旽子分明无疑。退溪及讷斋冲庵秋江诸说。当为定论。但元耘谷天锡野史。有祦实王氏之说。然元公是外人。亦何以真知实状。此必祦昌之党。做出腋下龙鳞之说。以诳诱一世。元公闻是说而信记之矣。此是千古疑案。故采附诸说于下。以备参考。退溪言行录。门人问祦昌实王氏。而 我朝修史。冒以伪辛。 先生答曰。大不然。若实王氏而后冒纂。则一史中前后设辞。岂无抵牾处。观史录。前后相符。无一可疑。般若事尤甚明验。又问李穑当立前王之子。圃隐冶隐之守节。果为辛氏耶。答曰。为此语者。固出于此。然不可以三人一时事。疑其不当疑。况虽辛氏。而吾王既以为子。则郑吉之事。固其所也。 朴讷斋祥撰东国史略。引牧隐尝语人曰。致堂胡氏。论晋元帝姓牛。东晋君臣。何以不革耶。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凭依旧业。安能系属人心。舍而刱初。难易绝矣。此亦乘势就事。不得已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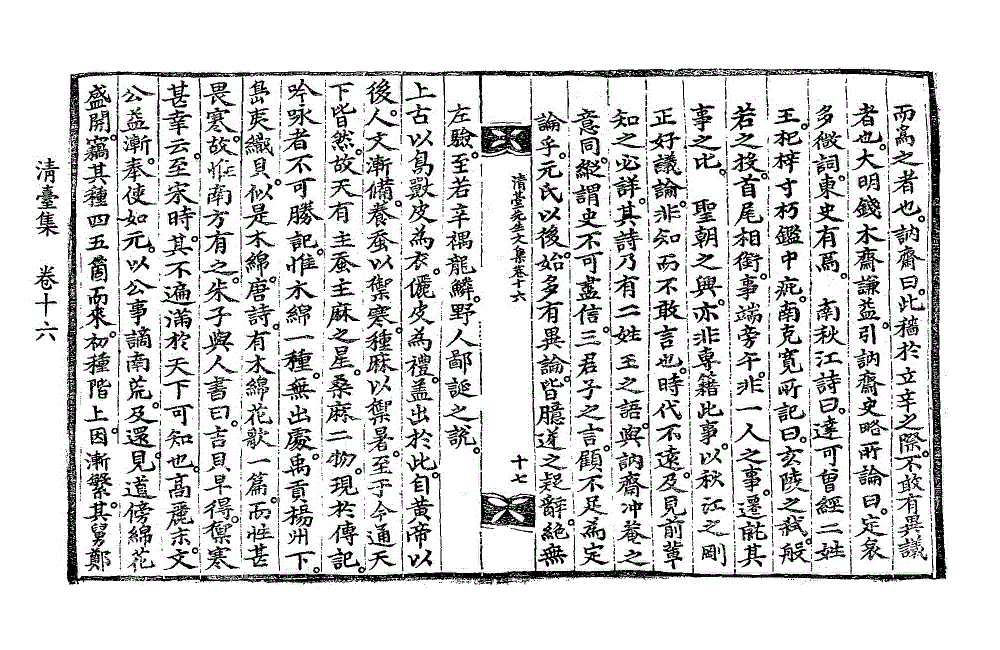 而为之者也。讷斋曰。此穑于立辛之际。不敢有异议者也。大明钱木斋谦益。引讷斋史略所论曰。定哀多微词。东史有焉。 南秋江诗曰。达可曾经二姓王。杞梓寸朽鉴中疵。南克宽所记曰。玄陵之弑。般若之投。首尾相衔。事端旁午。非一人之事。迁就其事之比。 圣朝之兴。亦非专籍此事。以秋江之刚正好议论。非知而不敢言也。时代不远。及见前辈知之必详。其诗乃有二姓王之语。与讷斋冲庵之意同。纵谓史不可尽信。三君子之言。顾不足为定论乎。元氏以后。始多有异论。皆臆逆之疑辞。绝无左验。至若辛祦龙鳞。野人鄙诞之说。
而为之者也。讷斋曰。此穑于立辛之际。不敢有异议者也。大明钱木斋谦益。引讷斋史略所论曰。定哀多微词。东史有焉。 南秋江诗曰。达可曾经二姓王。杞梓寸朽鉴中疵。南克宽所记曰。玄陵之弑。般若之投。首尾相衔。事端旁午。非一人之事。迁就其事之比。 圣朝之兴。亦非专籍此事。以秋江之刚正好议论。非知而不敢言也。时代不远。及见前辈知之必详。其诗乃有二姓王之语。与讷斋冲庵之意同。纵谓史不可尽信。三君子之言。顾不足为定论乎。元氏以后。始多有异论。皆臆逆之疑辞。绝无左验。至若辛祦龙鳞。野人鄙诞之说。上古以鸟兽皮为衣。俪皮为礼。盖出于此。自黄帝以后。人文渐备。养蚕以御寒。种麻以御暑。至于今通天下皆然。故天有主蚕主麻之星。桑麻二物。现于传记。吟咏者不可胜记。惟木绵一种。无出处。禹贡杨州下。岛夷织贝。似是木绵。唐诗。有木绵花歌一篇。而性甚畏寒。故惟南方有之。朱子与人书曰。吉贝早得。御寒甚幸云。至宋时。其不遍满于天下可知也。高丽末。文公益渐。奉使如元。以公事谪南荒。及还。见道傍绵花盛开。窃其种四五个而来。初种阶上。因渐繁。其舅郑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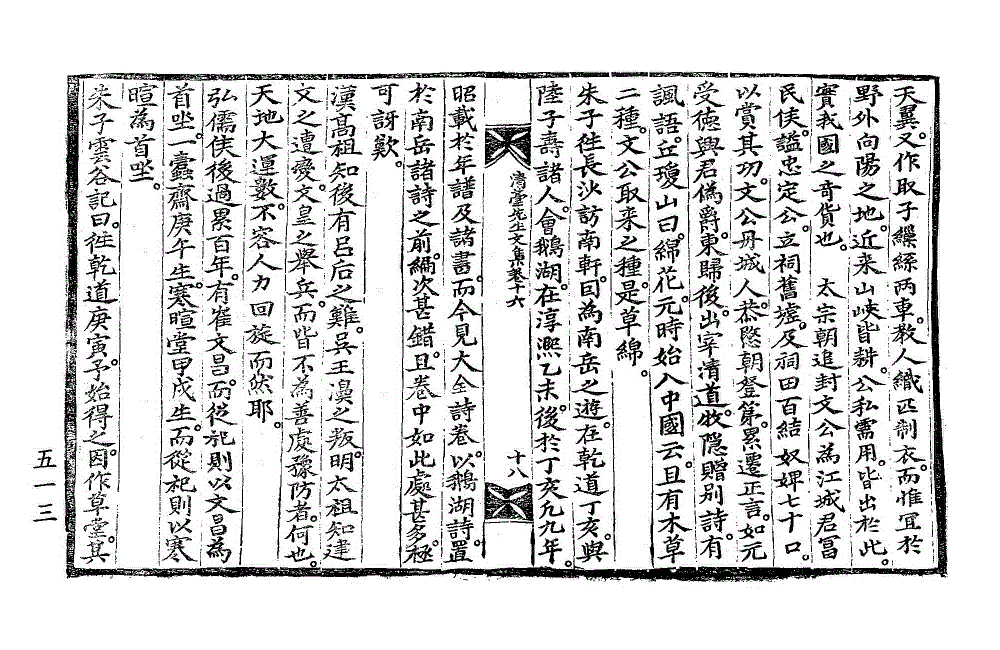 天翼。又作取子缫丝两车。教人织匹制衣。而惟宜于野外向阳之地。近来山峡皆耕。公私需用。皆出于此。实我国之奇货也。 太宗朝追封文公为江城君富民侯。谥忠定公。立祠旧墟。及祠田百结奴婢七十口。以赏其功。文公丹城人。恭悯朝登第。累迁正言。如元受德兴君伪爵。东归后。出宰清道。牧隐赠别诗。有讽语。丘琼山曰。绵花。元时始入中国云。且有木草二种。文公取来之种。是草绵。
天翼。又作取子缫丝两车。教人织匹制衣。而惟宜于野外向阳之地。近来山峡皆耕。公私需用。皆出于此。实我国之奇货也。 太宗朝追封文公为江城君富民侯。谥忠定公。立祠旧墟。及祠田百结奴婢七十口。以赏其功。文公丹城人。恭悯朝登第。累迁正言。如元受德兴君伪爵。东归后。出宰清道。牧隐赠别诗。有讽语。丘琼山曰。绵花。元时始入中国云。且有木草二种。文公取来之种。是草绵。朱子往长沙访南轩。因为南岳之游。在乾道丁亥。与陆子寿诸人。会鹅湖。在淳熙乙未。后于丁亥凡九年。昭载于年谱及诸书。而今见大全诗卷。以鹅湖诗。置于南岳诸诗之前。编次甚错。且卷中如此处甚多。极可讶叹。
汉高祖知后有吕后之难。吴王濞之叛。明太祖知建文之遭变。文皇之举兵。而皆不为善处豫防者。何也。天地大运数。不容人力回旋而然耶。
弘儒侯后过累百年。有崔文昌。而从祀则以文昌为首坐。一蠹斋庚午生。寒暄堂甲戌生。而从祀则以寒暄为首坐。
朱子云谷记曰。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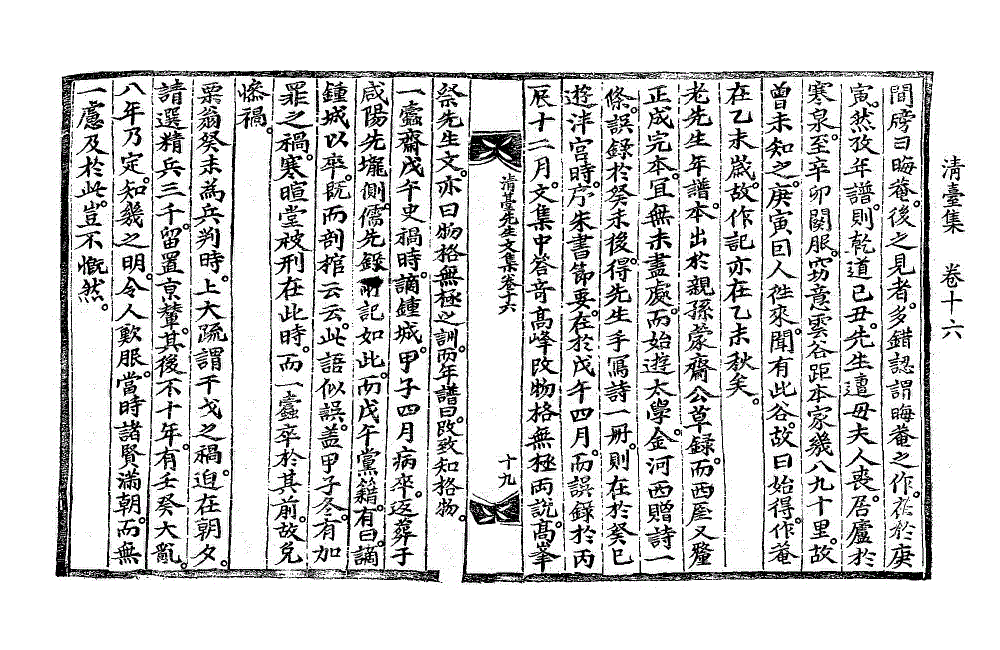 间榜曰晦庵。后之见者。多错认谓晦庵之作。在于庚寅。然孜年谱。则乾道己丑。先生遭母夫人丧。居庐于寒泉。至辛卯阕服。窃意云谷距本家几八九十里。故曾未知之。庚寅因人往来。闻有此谷。故曰始得。作庵在乙未岁。故作记亦在乙未秋矣。
间榜曰晦庵。后之见者。多错认谓晦庵之作。在于庚寅。然孜年谱。则乾道己丑。先生遭母夫人丧。居庐于寒泉。至辛卯阕服。窃意云谷距本家几八九十里。故曾未知之。庚寅因人往来。闻有此谷。故曰始得。作庵在乙未岁。故作记亦在乙未秋矣。老先生年谱。本出于亲孙蒙斋公草录。而西厓又釐正成完本。宜无未尽处。而始游太学。金河西赠诗一条。误录于癸未后。得先生手写诗一册。则在于癸巳游泮宫时。序朱书节要。在于戊午四月。而误录于丙辰十二月。文集中答奇高峰改物格无极两说。高峰祭先生文。亦曰物格无极之训。而年谱曰。改致知格物。
一蠹斋戊午史祸时。谪钟城。甲子四月病卒。返葬于咸阳先垄侧。儒先录所记如此。而戊午党籍。有曰。谪钟城以卒。既而剖棺云云。此语似误。盖甲子冬。有加罪之祸。寒暄堂被刑在此时。而一蠹卒于其前。故免惨祸。
栗翁癸未为兵判时。上大疏谓干戈之祸。迫在朝夕。请选精兵三千。留置京辇。其后不十年。有壬癸大乱。八年乃定。知几之明。令人叹服。当时诸贤满朝。而无一虑及于此。岂不慨然。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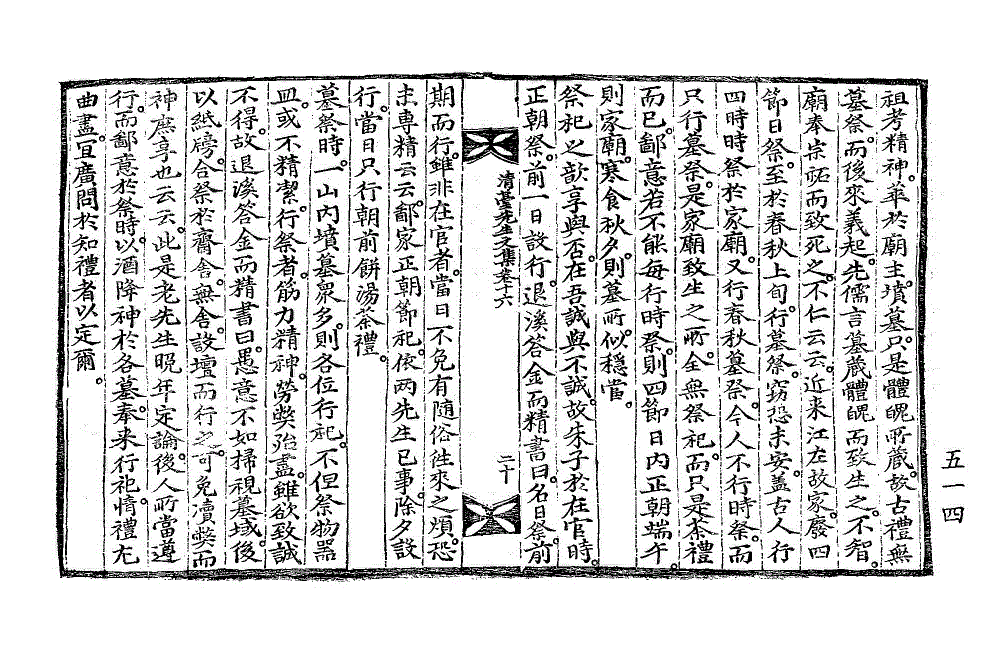 祖考精神。萃于庙主。坟墓。只是体魄所藏。故古礼无墓祭。而后来义起。先儒言墓藏体魄而致生之。不智。庙奉宗祏而致死之。不仁云云。近来江左故家。废四节日祭。至于春秋上旬。行墓祭。窃恐未安。盖古人行四时时祭于家庙。又行春秋墓祭。今人不行时祭。而只行墓祭。是家庙致生之所。全无祭祀。而只是茶礼而已。鄙意若不能每行时祭。则四节日内正朝端午。则家庙。寒食秋夕。则墓所。似稳当。
祖考精神。萃于庙主。坟墓。只是体魄所藏。故古礼无墓祭。而后来义起。先儒言墓藏体魄而致生之。不智。庙奉宗祏而致死之。不仁云云。近来江左故家。废四节日祭。至于春秋上旬。行墓祭。窃恐未安。盖古人行四时时祭于家庙。又行春秋墓祭。今人不行时祭。而只行墓祭。是家庙致生之所。全无祭祀。而只是茶礼而已。鄙意若不能每行时祭。则四节日内正朝端午。则家庙。寒食秋夕。则墓所。似稳当。祭祀之歆享与否。在吾诚与不诚。故朱子于在官时。正朝祭。前一日设行。退溪答金而精书曰。名日祭。前期而行。虽非在官者。当日不免有随俗往来之烦。恐未专精云云。鄙家正朝节祀。依两先生已事。除夕设行。当日只行朝前饼汤茶礼。
墓祭时。一山内坟墓众多。则各位行祀。不但祭物器皿。或不精洁。行祭者。筋力精神。劳弊殆尽。虽欲致诚不得。故退溪答金而精书曰。愚意不如扫视墓域。后以纸榜。合祭于斋舍。无舍。设坛而行之。可免渎弊而神庶享也云云。此是老先生晚年定论。后人所当遵行。而鄙意于祭时。以酒降神于各墓。奉来行祀。情礼尤曲尽。宜广问于知礼者以定尔。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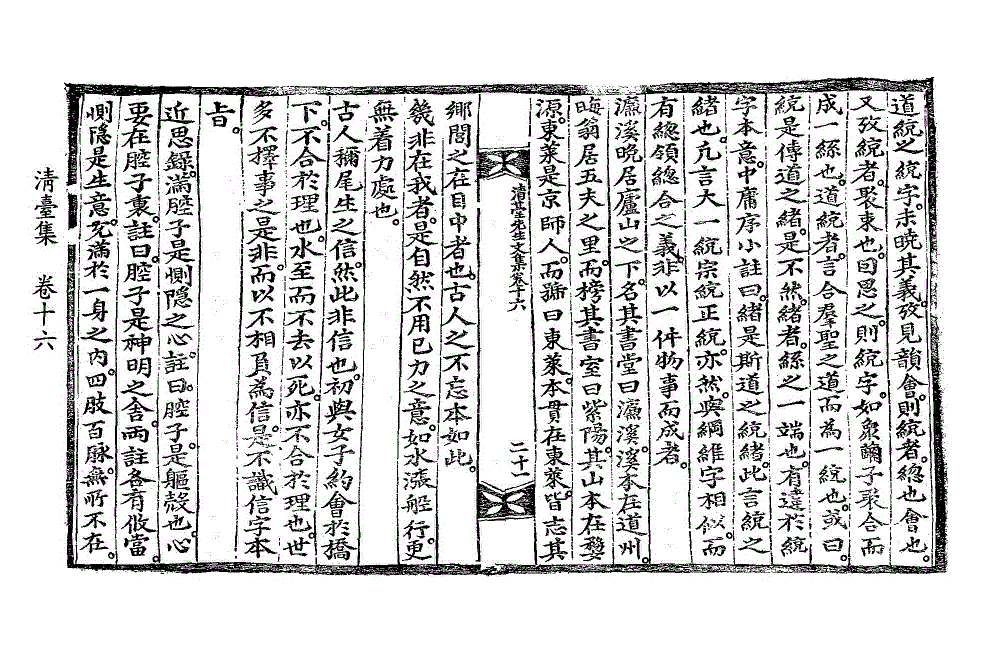 道统之统字。未晓其义。考见韵会。则统者。总也会也。又考统者。聚束也。因思之。则统字。如众茧子聚合而成一丝也。道统者。言合群圣之道而为一统也。或曰。统是传道之绪。是不然。绪者。丝之一端也。有违于统字本意。中庸序小注曰。绪是斯道之统绪。此言统之绪也。凡言大一统宗统正统。亦然。与纲维字相似。而有总领总合之义。非以一件物事而成者。
道统之统字。未晓其义。考见韵会。则统者。总也会也。又考统者。聚束也。因思之。则统字。如众茧子聚合而成一丝也。道统者。言合群圣之道而为一统也。或曰。统是传道之绪。是不然。绪者。丝之一端也。有违于统字本意。中庸序小注曰。绪是斯道之统绪。此言统之绪也。凡言大一统宗统正统。亦然。与纲维字相似。而有总领总合之义。非以一件物事而成者。濂溪晚居庐山之下。名其书堂曰濂溪。溪本在道州。晦翁居五夫之里。而榜其书室曰紫阳。其山本在㜈源。东莱是京师人。而号曰东莱。本贯在东莱。皆志其乡闾之在目中者也。古人之不忘本如此。
几非在我者。是自然不用己力之意。如水涨船行。更无着力处也。
古人称尾生之信。然此非信也。初与女子约会于桥下。不合于理也。水至而不去以死。亦不合于理也。世多不择事之是非。而以不相负为信。是不识信字本旨。
近思录。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注曰。腔子。是躯壳也。心要在腔子里。注曰。腔子是神明之舍。两注各有攸当。恻隐是生意。充满于一身之内。四肢百脉。无所不在。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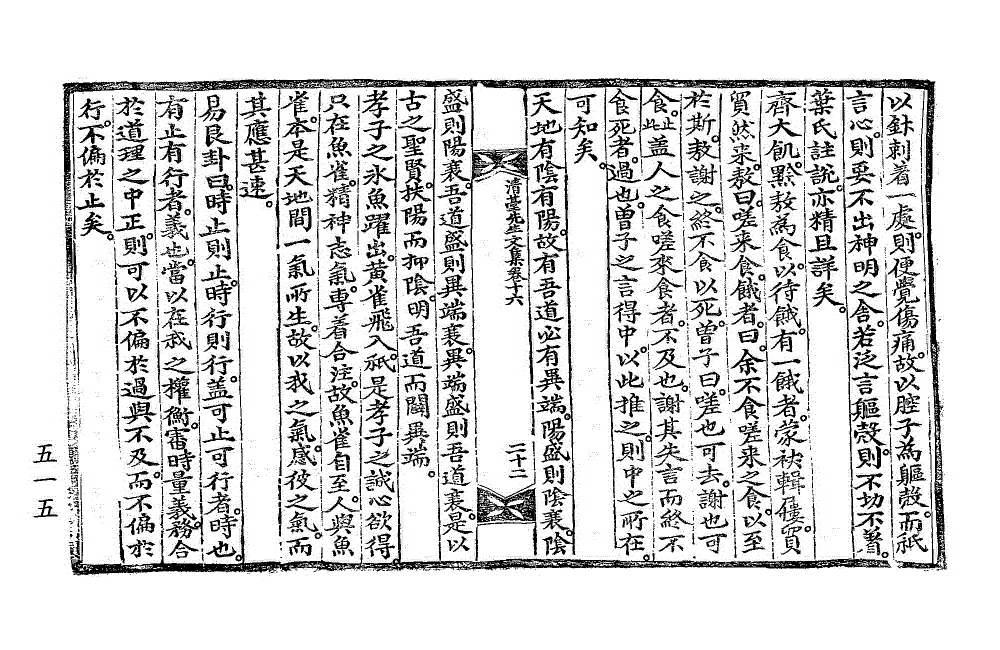 以针刺着一处。则便觉伤痛。故以腔子为躯壳。而秖言心。则要不出神明之舍。若泛言躯壳。则不切不着。叶氏注说。亦精且详矣。
以针刺着一处。则便觉伤痛。故以腔子为躯壳。而秖言心。则要不出神明之舍。若泛言躯壳。则不切不着。叶氏注说。亦精且详矣。齐大饥。黔敖为食。以待饿。有一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敖曰。嗟来食。饿者。曰。余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敖谢之。终不食以死。曾子曰。嗟也可去。谢也可食。(止此)盖人之食嗟来食者。不及也。谢其失言而终不食死者。过也。曾子之言得中。以此推之。则中之所在。可知矣。
天地有阴有阳。故有吾道必有异端。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吾道盛则异端衰。异端盛则吾道衰。是以古之圣贤。扶阳而抑阴。明吾道而辟异端。
孝子之冰鱼跃出。黄雀飞入。秖是孝子之诚心欲得。只在鱼雀。精神志气。专着合注。故鱼雀自至。人与鱼雀。本是天地间一气所生。故以我之气。感彼之气。而其应甚速。
易艮卦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盖可止可行者。时也。有止有行者。义也。当以在我之权衡。审时量义。务合于道理之中正。则可以不偏于过与不及。而不偏于行。不偏于止矣。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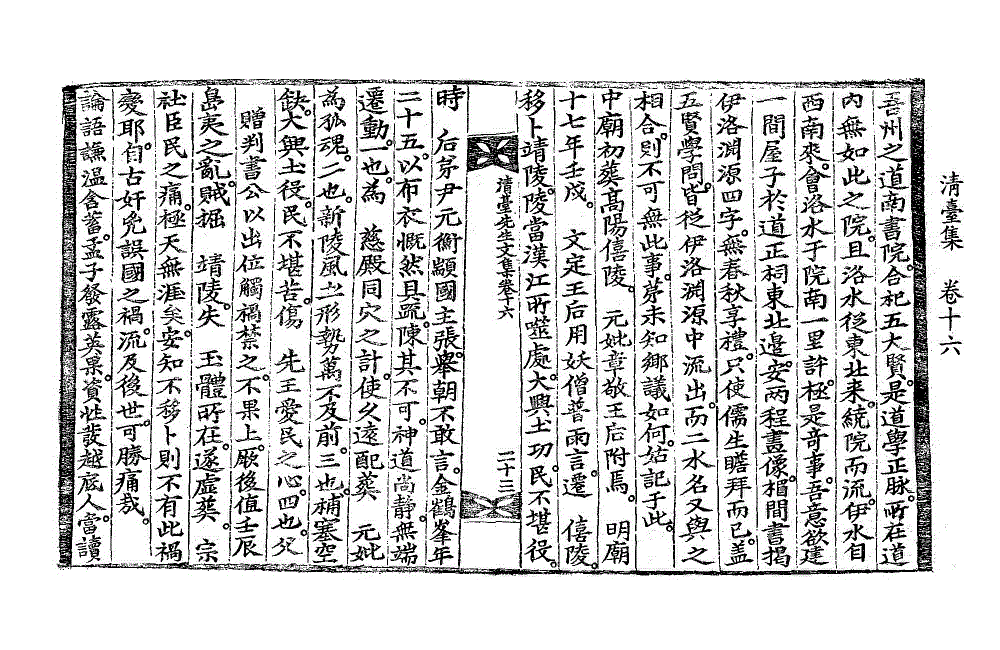 吾州之道南书院。合祀五大贤。是道学正脉。所在道内无如此之院。且洛水从东北来。绕院而流。伊水自西南来。会洛水于院南一里许。极是奇事。吾意欲建一间屋子于道正祠东北边。安两程画像。楣间书揭伊洛渊源四字。无春秋享礼。只使儒生瞻拜而已。盖五贤学问。皆从伊洛渊源中流出。而二水名又与之相合。则不可无此事。第未知乡议如何。姑记于此。
吾州之道南书院。合祀五大贤。是道学正脉。所在道内无如此之院。且洛水从东北来。绕院而流。伊水自西南来。会洛水于院南一里许。极是奇事。吾意欲建一间屋子于道正祠东北边。安两程画像。楣间书揭伊洛渊源四字。无春秋享礼。只使儒生瞻拜而已。盖五贤学问。皆从伊洛渊源中流出。而二水名又与之相合。则不可无此事。第未知乡议如何。姑记于此。中庙初葬高阳僖陵。 元妣章敬王后附焉。 明庙十七年壬戌。 文定王后用妖僧普雨言。迁 僖陵。移卜靖陵。陵当汉江所噬处。大兴土功。民不堪役。时 后弟尹元衡颛国主张。举朝不敢言。金鹤峰年二十五。以布衣慨然具疏。陈其不可。神道尚静。无端迁动。一也。为 慈殿同穴之计。使久远配葬 元妣为孤魂。二也。新陵风之形势万不及前。三也。补塞空缺。大兴土役。民不堪苦。伤 先王爱民之心。四也。父 赠判书公以出位触祸禁之。不果上。厥后值壬辰岛夷之乱。贼掘 靖陵。失 玉体所在。遂虚葬。 宗社臣民之痛。极天无涯矣。安知不移卜则不有此祸变耶。自古奸凶误国之祸。流及后世。可胜痛哉。
论语谦温含蓄。孟子发露英果。资性发越底人。当读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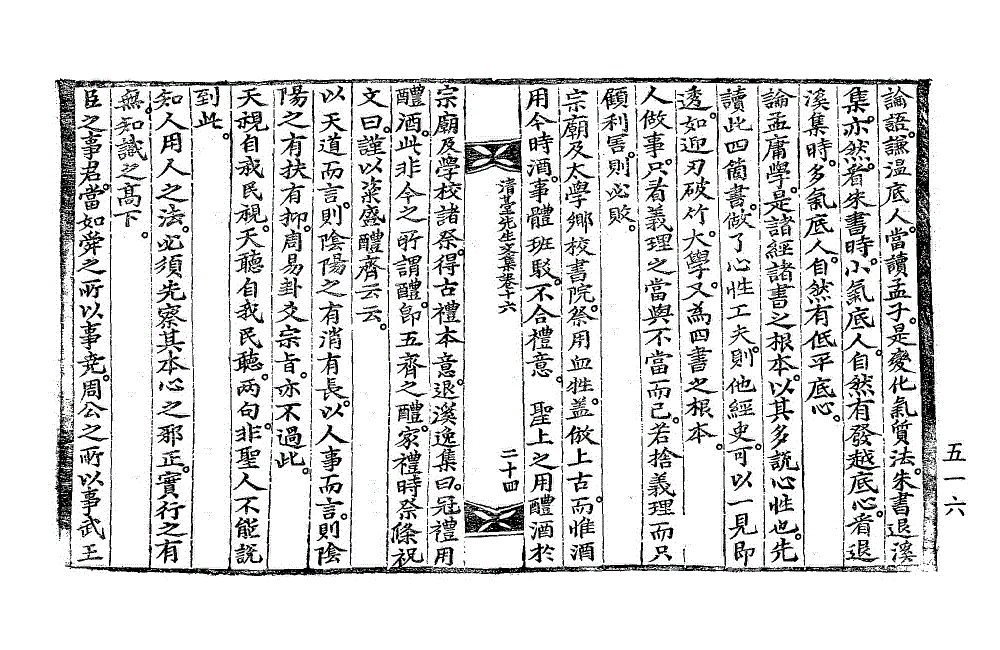 论语。谦温底人。当读孟子。是变化气质法。朱书退溪集。亦然。看朱书时。小气底人。自然有发越底心。看退溪集时。多气底人。自然有低平底心。
论语。谦温底人。当读孟子。是变化气质法。朱书退溪集。亦然。看朱书时。小气底人。自然有发越底心。看退溪集时。多气底人。自然有低平底心。论孟庸学。是诸经诸书之根本。以其多说心性也。先读此四个书。做了心性工夫。则他经史。可以一见即透。如迎刃破竹。大学。又为四书之根本。
人做事。只看义理之当与不当而已。若舍义理而只顾利害。则必败。
宗庙及太学乡校书院。祭用血牲。盖仿上古。而惟酒用今时酒。事体班驳。不合礼意。 圣上之用醴酒于宗庙及学校诸祭。得古礼本意。退溪逸集曰。冠礼用醴酒。此非今之所谓醴。即五齐之醴。家礼时祭条祝文曰。谨以粢盛醴齐云云。
以天道而言。则阴阳之有消有长。以人事而言。则阴阳之有扶有抑。周易卦爻宗旨。亦不过此。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两句。非圣人不能说到此。
知人用人之法。必须先察其本心之邪正。实行之有无。知识之高下。
臣之事君。当如舜之所以事尧。周公之所以事武王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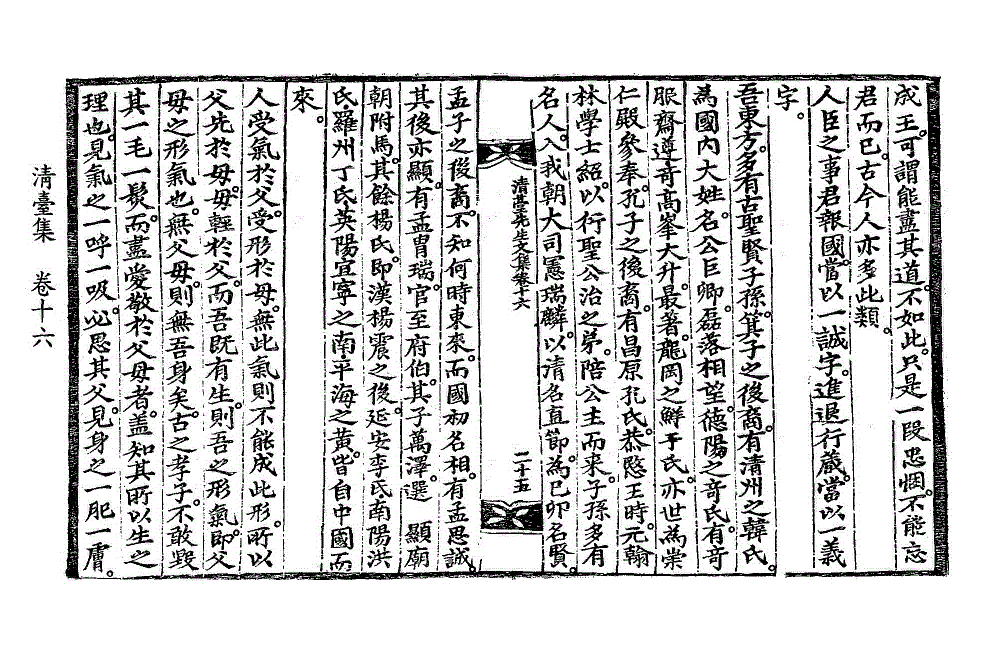 成王。可谓能尽其道。不如此。只是一段忠悃。不能忘君而已。古今人亦多此类。
成王。可谓能尽其道。不如此。只是一段忠悃。不能忘君而已。古今人亦多此类。人臣之事君报国。当以一诚字。进退行藏。当以一义字。
吾东方。多有古圣贤子孙。箕子之后裔。有清州之韩氏。为国内大姓。名公巨卿。磊落相望。德阳之奇氏。有奇服斋遵,奇高峰大升。最著。龙冈之鲜于氏。亦世为崇仁殿参奉。孔子之后裔。有昌原孔氏。恭悯王时。元翰林学士绍。以衍圣公治之弟。陪公主而来。子孙多有名人。入我朝大司宪瑞麟。以清名直节。为己卯名贤。孟子之后裔。不知何时东来。而国初名相。有孟思诚。其后亦显。有孟胄瑞。官至府伯。其子万泽。选 显庙朝附马。其馀杨氏。即汉杨震之后。延安李氏,南阳洪氏,罗州丁氏,英阳宜宁之南,平海之黄。皆自中国而来。
人受气于父。受形于母。无此气则不能成此形。所以父先于母。母轻于父。而吾既有生。则吾之形气。即父母之形气也。无父母。则无吾身矣。古之孝子。不敢毁其一毛一发。而尽爱敬于父母者。盖知其所以生之理也。见气之一呼一吸。必思其父。见身之一肌一肤。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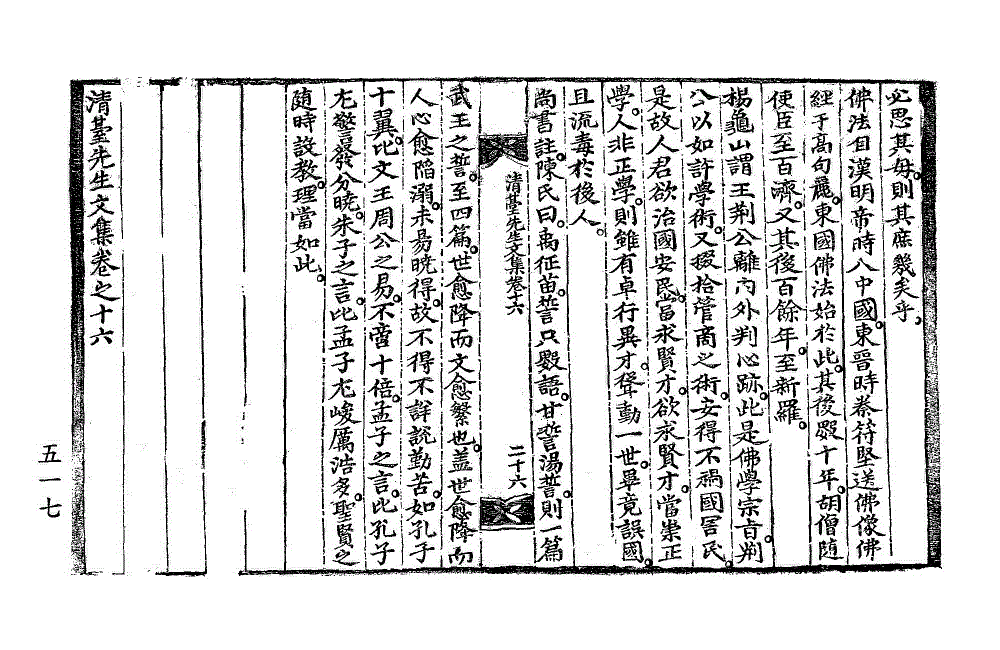 必思其母。则其庶几矣乎。
必思其母。则其庶几矣乎。佛法自汉明帝时入中国。东晋时秦苻坚送佛像佛经于高句丽。东国佛法始于此。其后数十年。胡僧随使臣至百济。又其后百馀年。至新罗。
杨龟山谓王荆公离内外判心迹。此是佛学宗旨。荆公以如许学术。又掇拾管商之术。安得不祸国害民。是故人君欲治国安民。当求贤才。欲求贤才。当崇正学。人非正学。则虽有卓行异才。耸动一世。毕竟误国。且流毒于后人。
尚书注。陈氏曰。禹征苗。誓只数语。甘誓汤誓。则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盖世愈降而人心愈陷溺。未易晓得。故不得不详说勤苦。如孔子十翼。比文王周公之易。不啻十倍。孟子之言。比孔子尤警发分晓。朱子之言。比孟子尤峻厉浩多。圣贤之随时设教。理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