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x 页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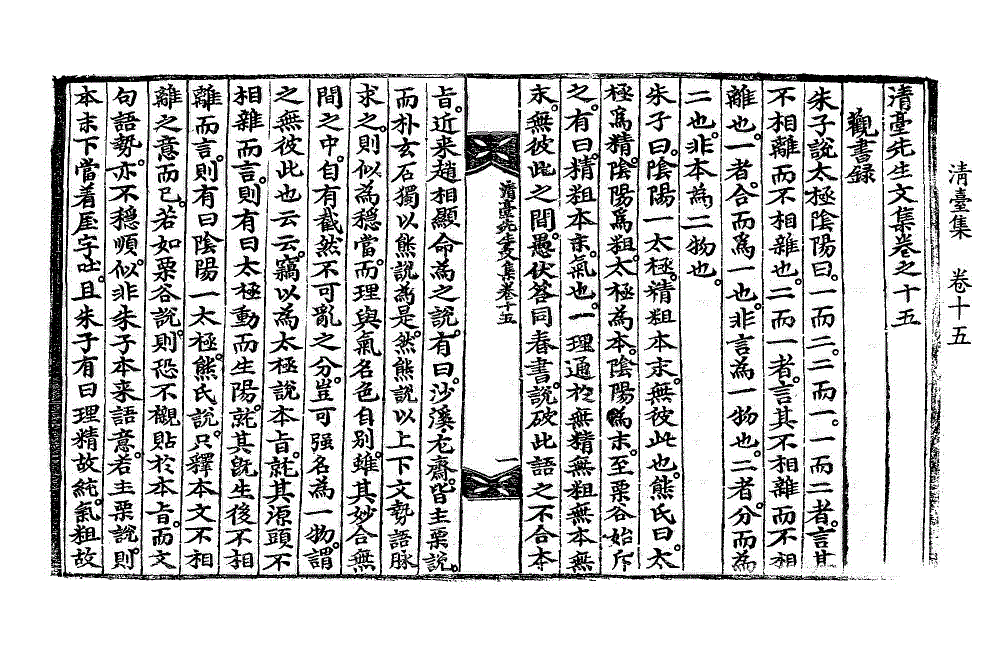 观书录
观书录朱子说太极阴阳曰。一而二。二而一。一而二者。言其不相离而不相杂也。二而一者。言其不相杂而不相离也。一者。合而为一也。非言为一物也。二者。分而为二也。非本为二物也。
朱子曰。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熊氏曰。太极为精。阴阳为粗。太极为本。阴阳为末。至栗谷始斥之。有曰。精粗本末。气也。一理通于无精无粗无本无末。无彼此之间。愚伏答同春书。说破此语之不合本旨。近来赵相显命为之说。有曰。沙溪,尤斋。皆主栗说。而朴玄石独以熊说为是。然熊说以上下文势语脉求之。则似为稳当。而理与气名色自别。虽其妙合无间之中。自有截然不可乱之分。岂可强名为一物。谓之无彼此也云云。窃以为太极说本旨。就其源头不相杂而言。则有曰太极动而生阳。就其既生后不相离而言。则有曰阴阳一太极。熊氏说。只释本文不相离之意而已。若如栗谷说。则恐不衬贴于本旨。而文句语势。亦不稳顺。似非朱子本来语意。若主栗说。则本末下当着厓字吐。且朱子有曰理精故纯。气粗故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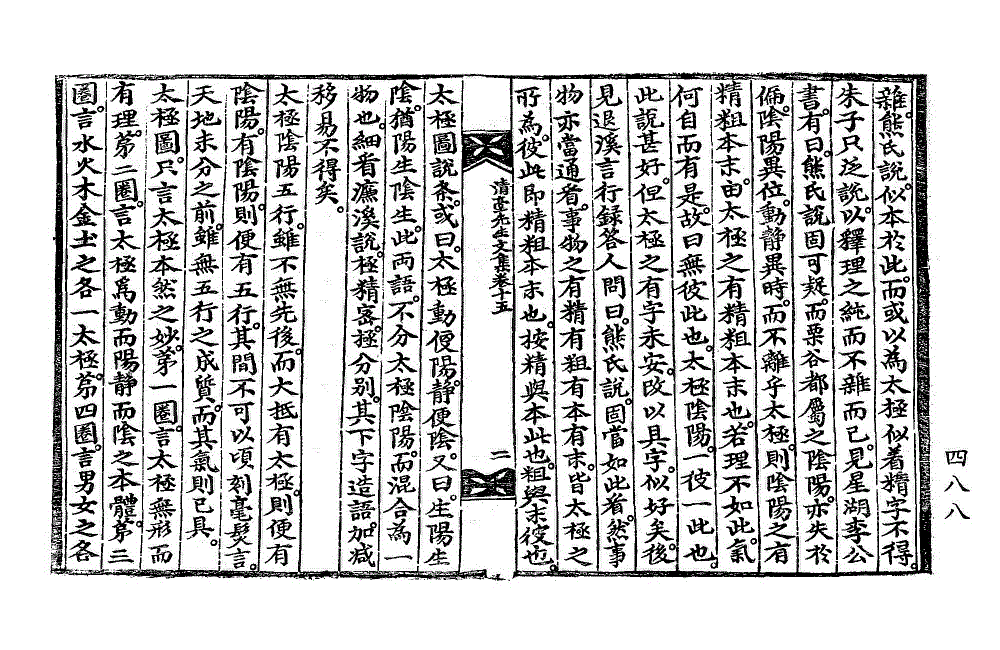 杂。熊氏说。似本于此。而或以为太极似着精字不得。朱子只泛说。以释理之纯而不杂而已。见星湖李公书。有曰。熊氏说固可疑。而栗谷都属之阴阳。亦失于偏。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不离乎太极。则阴阳之有精粗本末。由太极之有精粗本末也。若理不如此。气何自而有是。故曰无彼此也。太极阴阳。一彼一此也。此说甚好。但太极之有字未安。改以具字。似好矣。后见退溪言行录答人问曰。熊氏说。固当如此看。然事物亦当通看。事物之有精有粗有本有末。皆太极之所为。彼此即精粗本末也。按精与本此也。粗与末彼也。
杂。熊氏说。似本于此。而或以为太极似着精字不得。朱子只泛说。以释理之纯而不杂而已。见星湖李公书。有曰。熊氏说固可疑。而栗谷都属之阴阳。亦失于偏。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不离乎太极。则阴阳之有精粗本末。由太极之有精粗本末也。若理不如此。气何自而有是。故曰无彼此也。太极阴阳。一彼一此也。此说甚好。但太极之有字未安。改以具字。似好矣。后见退溪言行录答人问曰。熊氏说。固当如此看。然事物亦当通看。事物之有精有粗有本有末。皆太极之所为。彼此即精粗本末也。按精与本此也。粗与末彼也。太极图说条。或曰。太极动便阳。静便阴。又曰。生阳生阴。犹阳生阴生。此两语。不分太极阴阳。而混合为一物也。细看濂溪说。极精密。极分别。其下字造语。加减移易不得矣。
太极阴阳五行。虽不无先后。而大抵有太极。则便有阴阳。有阴阳。则便有五行。其间不可以顷刻毫发言。天地未分之前。虽无五行之成质。而其气则已具。
太极图。只言太极本然之妙。第一圈。言太极无形而有理。第二圈。言太极为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第三圈。言水火木金土之各一太极。第四圈。言男女之各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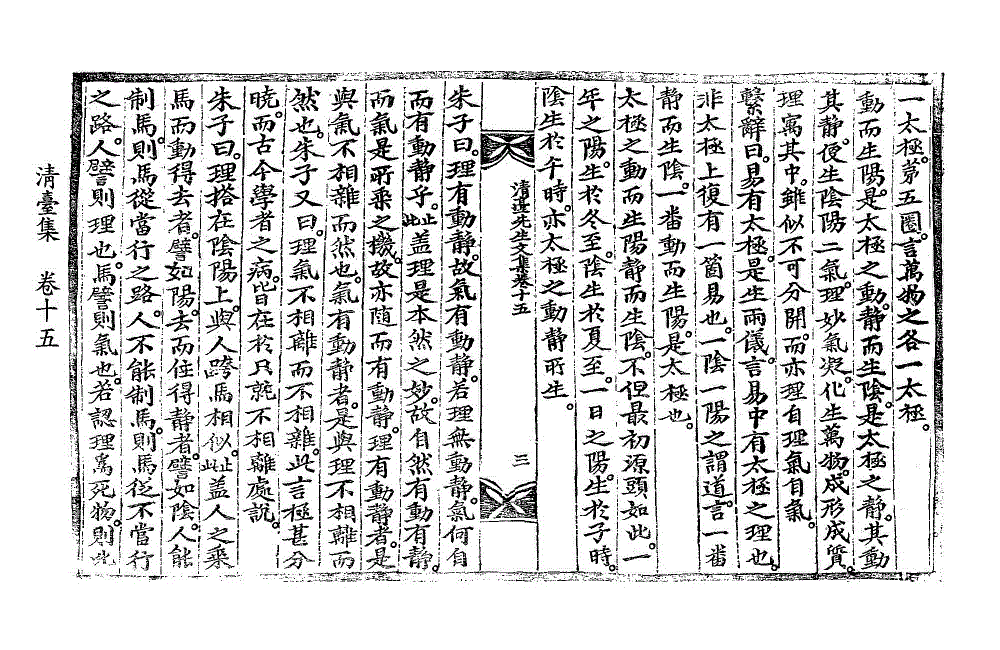 一太极。第五圈。言万物之各一太极。
一太极。第五圈。言万物之各一太极。动而生阳。是太极之动。静而生阴。是太极之静。其动其静。便生阴阳二气。理妙气凝。化生万物。成形成质。理寓其中。虽似不可分开。而亦理自理气自气。
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言易中有太极之理也。非太极上复有一个易也。一阴一阳之谓道。言一番静而生阴。一番动而生阳。是太极也。
太极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但最初源头如此。一年之阳。生于冬至。阴生于夏至。一日之阳。生于子时。阴生于午时。亦太极之动静所生。
朱子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止此)盖理是本然之妙。故自然有动有静。而气是所乘之机。故亦随而有动静。理有动静者。是与气不相杂而然也。气有动静者。是与理不相离而然也。朱子又曰。理气不相离而不相杂。此言极甚分晓。而古今学者之病。皆在于只就不相离处说。
朱子曰。理搭在阴阳上。与人跨马相似。(止此)盖人之乘马而动得去者。譬如阳。去而住得静者。譬如阴。人能制马。则马从当行之路。人不能制马。则马从不当行之路。人譬则理也。马譬则气也。若认理为死物。则比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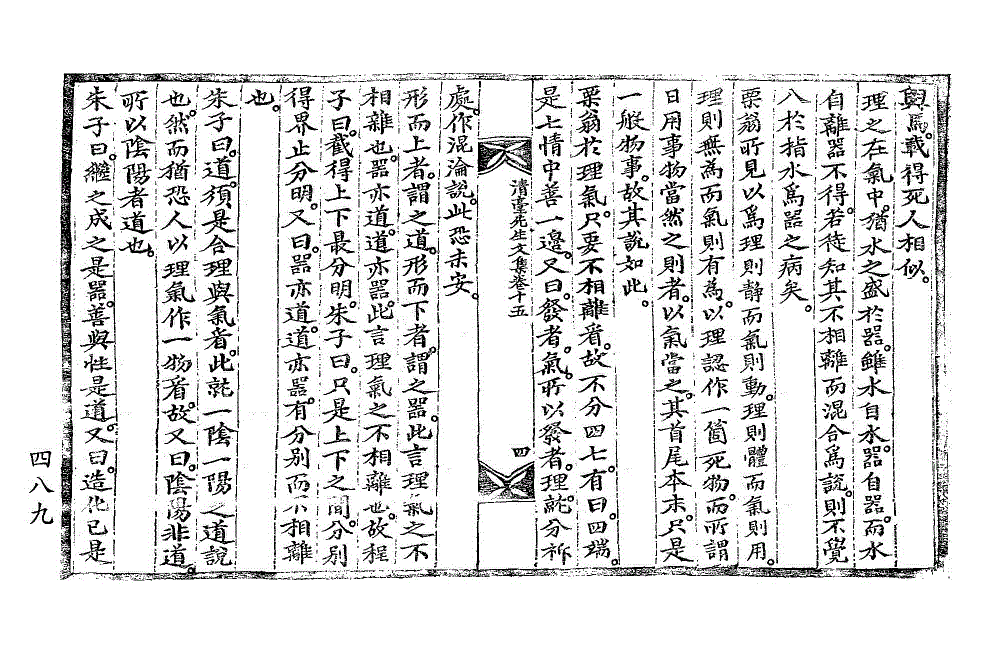 与马。载得死人相似。
与马。载得死人相似。理之在气中。犹水之盛于器。虽水自水。器自器。而水自离器不得。若徒知其不相离而混合为说。则不觉入于指水为器之病矣。
栗翁所见以为理则静而气则动。理则体而气则用。理则无为而气则有为。以理认作一个死物。而所谓日用事物当然之则者。以气当之。其首尾本末。只是一般物事。故其说如此。
栗翁于理气。只要不相离看。故不分四七。有曰。四端。是七情中善一边。又曰。发者。气。所以发者。理。就分析处。作混沦说。此恐未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此言理气之不相杂也。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气之不相离也。故程子曰。截得上下最分明。朱子曰。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界止分明。又曰。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朱子曰。道。须是合理与气看。此就一阴一阳之道说也。然而犹恐人以理气作一物看。故又曰。阴阳非道。所以阴阳者道也。
朱子曰。继之成之是器。善与性是道。又曰。造化已是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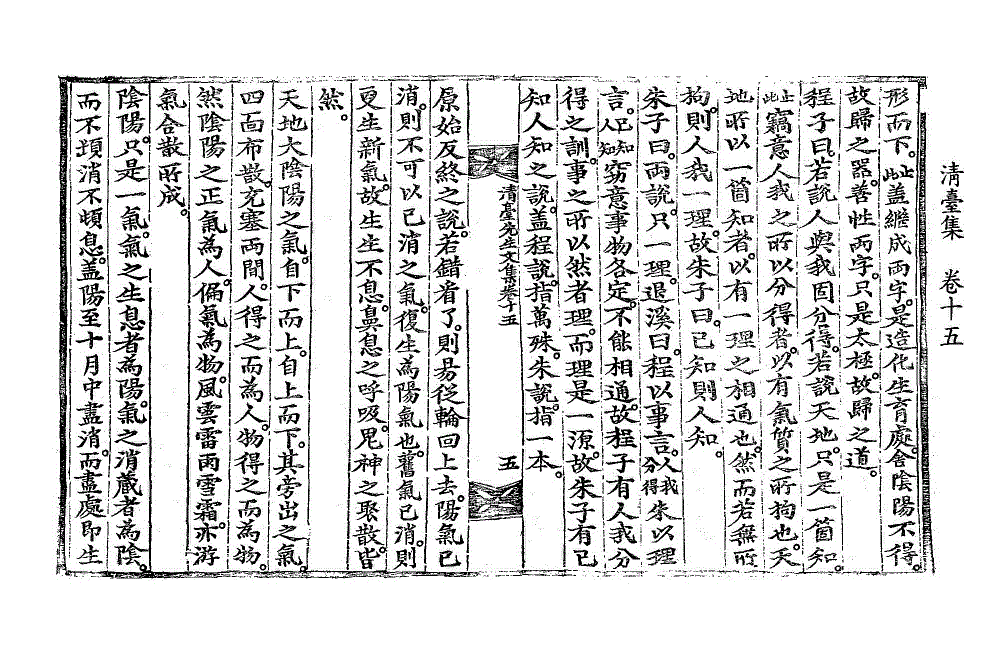 形而下。(止此)盖继成两字。是造化生育处。舍阴阳不得。故归之器。善性两字。只是太极。故归之道。
形而下。(止此)盖继成两字。是造化生育处。舍阴阳不得。故归之器。善性两字。只是太极。故归之道。程子曰。若说人与我固分得。若说天地。只是一个知。(止此)窃意人我之所以分得者。以有气质之所拘也。天地所以一个知者。以有一理之相通也。然而若无所拘。则人我一理。故朱子曰。己知则人知。
朱子曰。两说。只一理。退溪曰。程以事言。(人我分得)朱以理言。(己知人知)窃意事物各定。不能相通。故程子有人我分得之训。事之所以然者理。而理是一源。故朱子有己知人知之说。盖程说。指万殊。朱说。指一本。
原始反终之说。若错看了。则易从轮回上去。阳气已消。则不可以已消之气。复生为阳气也。旧气已消。则更生新气。故生生不息。鼻息之呼吸。鬼神之聚散。皆然。
天地大阴阳之气。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其旁出之气。四面布散。充塞两间。人得之而为人。物得之而为物。然阴阳之正气为人。偏气为物。风云雷雨雪霜。亦游气合散所成。
阴阳。只是一气。气之生息者为阳。气之消藏者为阴。而不顿消不顿息。盖阳至十月中尽消。而尽处即生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0L 页
 一分。一日长一分。满三十日则为三十分。而至冬至。始生一阳。阴爻亦然。而圣人扶阳抑阴。故阳始生。则静而养之。犹恐其或伤。阴始生则恶而戒之。犹恐其或长。大抵阴阳之气。消长不常。而其消也有渐。其长也亦有渐。古人曰。天地之道浸。浸者渐也。
一分。一日长一分。满三十日则为三十分。而至冬至。始生一阳。阴爻亦然。而圣人扶阳抑阴。故阳始生。则静而养之。犹恐其或伤。阴始生则恶而戒之。犹恐其或长。大抵阴阳之气。消长不常。而其消也有渐。其长也亦有渐。古人曰。天地之道浸。浸者渐也。流行主于动。故先言阳。对待主于静。故先言阴。流行不已而变易无穷。则是阳为之主也。对待一定而不可移易。则是阴为之主也。
天地间。有阴阳二气。而阴性湿。阳性燥。然燥湿相仍。燥极则湿生。湿极则燥生。且燥中有湿。湿中有燥。以河图言之。阴水生于阳位。阳火生于阴位。
感应之理。盖出于阴阳。阳极则感而召阴。阴极则感而召阳。人事之吉福属阳。凶祸属阴。如水旱风雨凡百感应。皆是阴阳。
通川。有丛石亭。众石皆六面。若斧斲㨾。盖石是阴气所结。阴数六。故自然如此。非天下之石皆然。独此处全露天机而然。余观大麦全禀阴气。故遇火而死。有一种麦。独六面。俗称六棱麦。其理与丛石一般。
阴太盛则为水灾。阳太盛则为旱灾。皆不能相和而然。盖阴阳不和。则为水旱而为饥为馑。为戾气而为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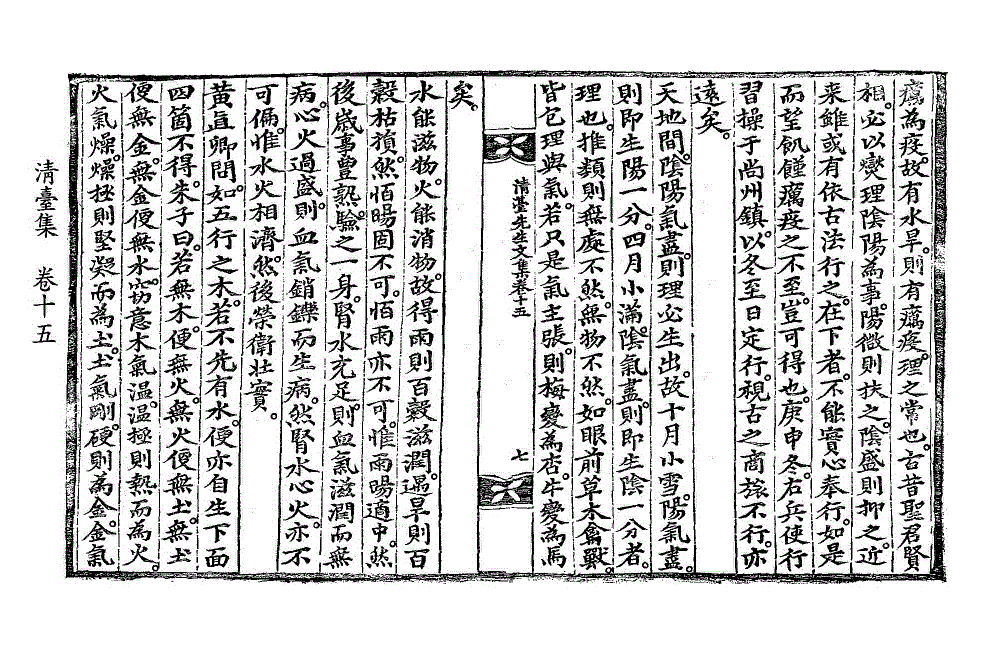 疠为疫。故有水旱。则有疠疫。理之常也。古昔圣君贤相。必以燮理阴阳为事。阳微则扶之。阴盛则抑之。近来虽或有依古法行之。在下者。不能实心奉行。如是而望饥馑疠疫之不至。岂可得也。庚申冬。右兵使行习操于尚州镇。以冬至日定行。视古之商旅不行。亦远矣。
疠为疫。故有水旱。则有疠疫。理之常也。古昔圣君贤相。必以燮理阴阳为事。阳微则扶之。阴盛则抑之。近来虽或有依古法行之。在下者。不能实心奉行。如是而望饥馑疠疫之不至。岂可得也。庚申冬。右兵使行习操于尚州镇。以冬至日定行。视古之商旅不行。亦远矣。天地间。阴阳气尽。则理必生出。故十月小雪。阳气尽。则即生阳一分。四月小满。阴气尽。则即生阴一分者。理也。推类则无处不然。无物不然。如眼前草木禽兽。皆包理与气。若只是气主张。则梅变为杏。牛变为马矣。
水能滋物。火能消物。故得雨则百谷滋润。遇旱则百谷枯损。然恒旸固不可。恒雨亦不可。惟雨旸适中。然后岁事礼熟。验之一身。肾水充足。则血气滋润而无病。心火过盛。则血气销铄而生病。然肾水心火。亦不可偏。惟水火相济。然后荣卫壮实。
黄直卿问。如五行之木。若不先有水。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朱子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窃意木气温。温极则热而为火。火气燥。燥极则坚凝而为土。土气刚。硬则为金。金气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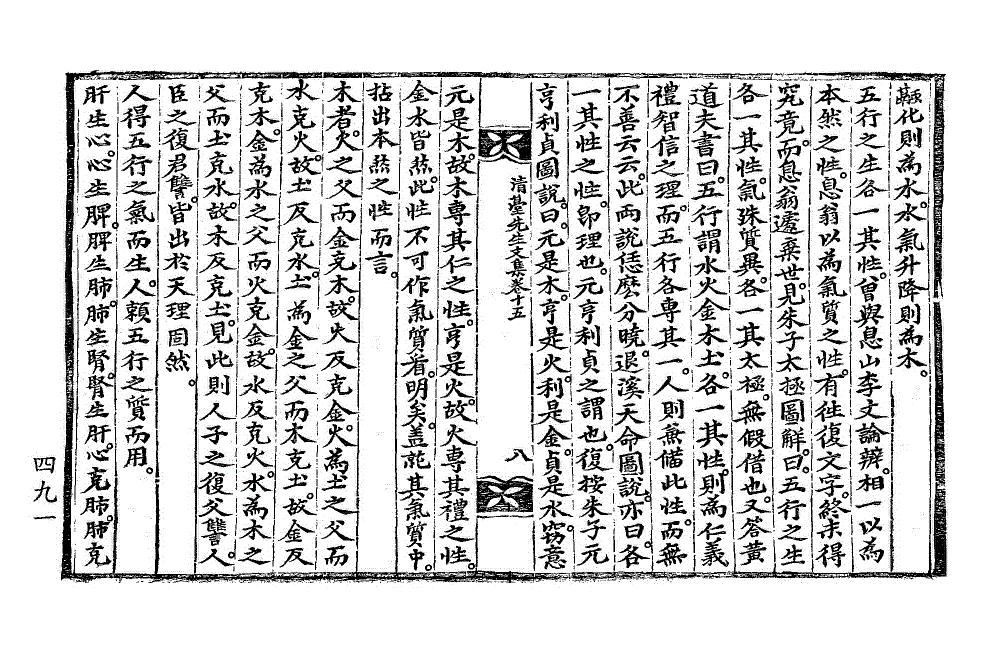 融化则为水。水气升降则为木。
融化则为水。水气升降则为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曾与息山李丈论辨。相一以为本然之性。息翁以为气质之性。有往复文字。终未得究竟。而息翁遽弃世。见朱子太极图解。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气殊质异。各一其太极。无假借也。又答黄道夫书曰。五行谓水火金木土。各一其性。则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则兼备此性。而无不善云云。此两说恁么分晓。退溪天命图说。亦曰。各一其性之性。即理也。元亨利贞之谓也。复按朱子元亨利贞图说。曰。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贞是水。窃意元是木。故木专其仁之性。亨是火。故火专其礼之性。金水皆然。此性不可作气质看。明矣。盖就其气质中。拈出本然之性而言。
木者。火之父而金克木。故火反克金。火为土之父而水克火。故土反克水。土为金之父而木克土。故金反克木。金为水之父而火克金。故水反克火。水为木之父而土克水。故木反克土。见此则人子之复父雠。人臣之复君雠。皆出于天理固然。
人得五行之气而生。人赖五行之质而用。
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生肝。心克肺。肺克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2H 页
 肝。肝克脾。脾克肾。肾克心。五脏生克。与五行同。
肝。肝克脾。脾克肾。肾克心。五脏生克。与五行同。朱子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退溪曰。正谓动者是心。而其所以动之故是性云耳。又曰。性非有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性具于心。而不能自发而自做。其主宰运用。实在于心云云。又曰。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说。是就心中。分理气言。与今所指心性说不同云。窃意动处动底。是从不相离处说。理发气发。是从不相杂处说。先儒言情者。性之自然发出。而因心以动。盖因心以动。则可谓动处是心也。由性发出。则可谓动底是性也。然而四端是本然之性所发。故曰理发。七情是气质之性所发。故曰气发。
韩久庵曰。栗谷谓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如此则理只为前所以然之故。而于后所当然之则。脉络不通。久庵此说甚好。盖言所以然者。体也。所当然者。用也。若如栗说。则是理虽为体。而于用处。专是气主张。而理不得干涉也。
人心听命于道心则似道心。而毕竟是声色臭味所生。不可谓道心。七情顺理而发则似四端。而毕竟是喜怒哀乐所发。不可谓四端。
朱子曰。只是一个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此等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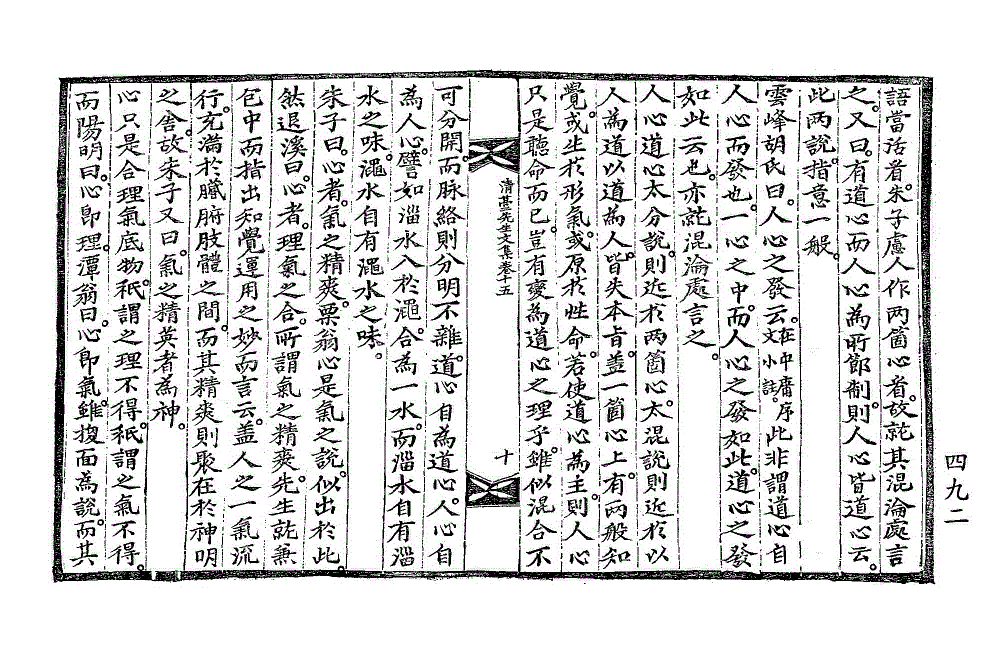 语当活看。朱子虑人作两个心看。故就其混沦处言之。又曰。有道心而人心为所节制。则人心皆道心云。此两说。指意一般。
语当活看。朱子虑人作两个心看。故就其混沦处言之。又曰。有道心而人心为所节制。则人心皆道心云。此两说。指意一般。云峰胡氏曰。人心之发云。(在中庸序文小注。)此非谓道心自人心而发也。一心之中。而人心之发如此。道心之发如此云也。亦就混沦处言之。
人心道心太分说。则近于两个心。太混说则近于以人为道以道为人。皆失本旨。盖一个心上。有两般知觉。或生于形气。或原于性命。若使道心为主。则人心只是听命而已。岂有变为道心之理乎。虽似混合不可分开。而脉络则分明不杂。道心自为道心。人心自为人心。譬如淄水入于渑。合为一水。而淄水自有淄水之味。渑水自有渑水之味。
朱子曰。心者。气之精爽。栗翁心是气之说。似出于此。然退溪曰。心者。理气之合。所谓气之精爽。先生就兼包中而指出知觉运用之妙而言云。盖人之一气流行。充满于脏腑肢体之间。而其精爽则聚在于神明之舍。故朱子又曰。气之精英者为神。
心只是合理气底物。秖谓之理不得。秖谓之气不得。而阳明曰。心即理。潭翁曰。心即气。虽换面为说。而其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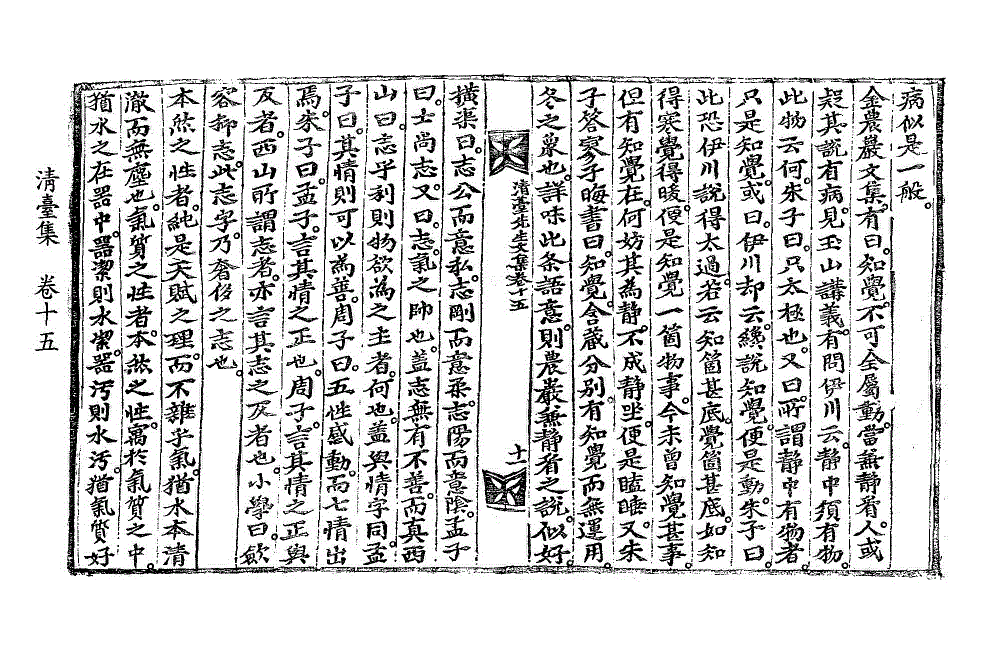 病似是一般。
病似是一般。金农岩文集。有曰。知觉。不可全属动。当兼静看。人或疑其说有病。见玉山讲义。有问伊川云。静中须有物。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极也。又曰。所谓静中有物者。只是知觉。或曰。伊川却云。才说知觉。便是动。朱子曰。此恐伊川说得太过。若云知个甚底。觉个甚底。如知得寒觉得暖。便是知觉一个物事。今未曾知觉甚事。但有知觉在。何妨其为静。不成静坐。便是瞌睡。又朱子答寥子晦书曰。知觉。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详味此条语意。则农岩兼静看之说。似好。
横渠曰。志公而意私。志刚而意柔。志阳而意阴。孟子曰。士尚志。又曰。志。气之帅也。盖志无有不善。而真西山曰。志乎利则物欲为之主者。何也。盖与情字同。孟子曰。其情则可以为善。周子曰。五性感动。而七情出焉。朱子曰。孟子。言其情之正也。周子。言其情之正与反者。西山所谓志者。亦言其志之反者也。小学曰。敛容抑志。此志字。乃奢侈之志也。
本然之性者。纯是天赋之理。而不杂乎气。犹水本清澈而无尘也。气质之性者。本然之性。寓于气质之中。犹水之在器中。器洁则水洁。器污则水污。犹气质好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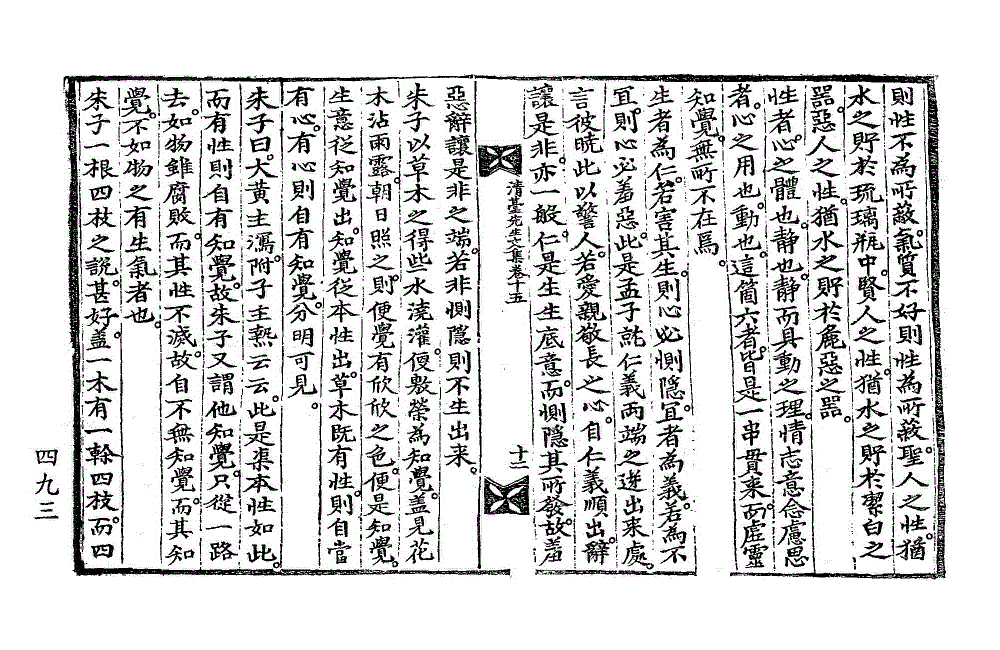 则性不为所蔽。气质不好则性为所蔽。圣人之性。犹水之贮于琉璃瓶中。贤人之性。犹水之贮于洁白之器。恶人之性。犹水之贮于粗恶之器。
则性不为所蔽。气质不好则性为所蔽。圣人之性。犹水之贮于琉璃瓶中。贤人之性。犹水之贮于洁白之器。恶人之性。犹水之贮于粗恶之器。性者。心之体也。静也。静而具动之理。情志意念虑思者。心之用也。动也。这个六者。皆是一串贯来。而虚灵知觉。无所不在焉。
生者为仁。若害其生。则心必恻隐。宜者为义。若为不宜。则心必羞恶。此是孟子就仁义两端之迸出来处。言彼晓此以警人。若爱亲敬长之心。自仁义顺出。辞让是非。亦一般。仁是生生底意。而恻隐其所发。故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若非恻隐则不生出来。
朱子以草木之得些水浇灌。便敷荣为知觉。盖见花木沾雨露。朝日照之。则便觉有欣欣之色。便是知觉。生意从知觉出。知觉从本性出。草木既有性。则自当有心。有心则自有知觉。分明可见。
朱子曰。大黄主泻。附子主热云云。此是渠本性如此。而有性则自有知觉。故朱子又谓他知觉。只从一路去。如物虽腐败。而其性不灭。故自不无知觉。而其知觉。不如物之有生气者也。
朱子一根四枝之说。甚好。盖一木有一干四枝。而四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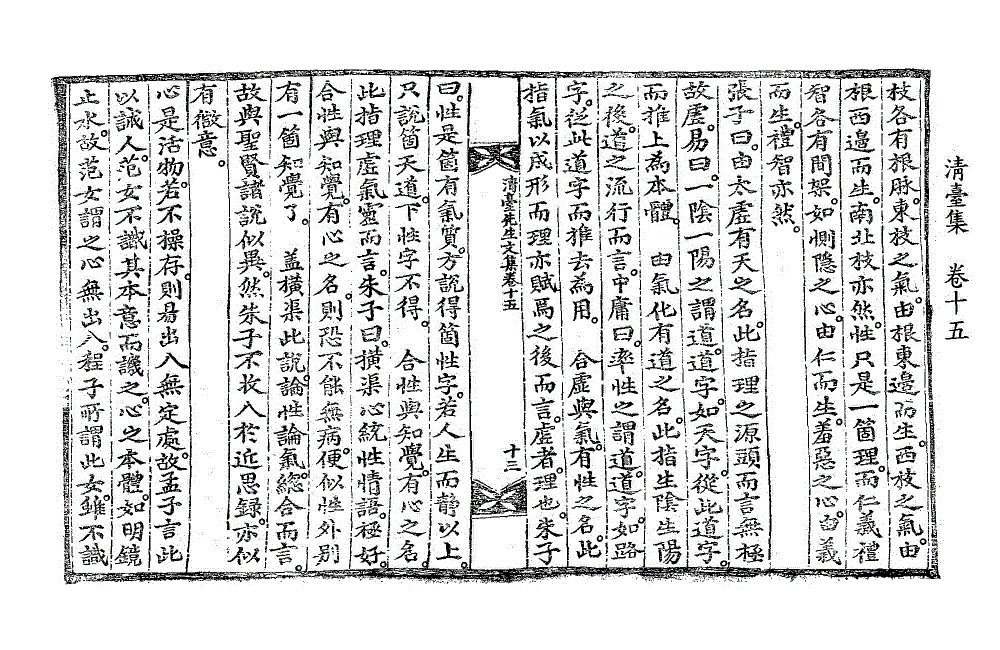 枝各有根脉。东枝之气。由根东边而生。西枝之气。由根西边而生。南北枝亦然。性只是一个理。而仁义礼智各有间架。如恻隐之心。由仁而生。羞恶之心。由义而生。礼智亦然。
枝各有根脉。东枝之气。由根东边而生。西枝之气。由根西边而生。南北枝亦然。性只是一个理。而仁义礼智各有间架。如恻隐之心。由仁而生。羞恶之心。由义而生。礼智亦然。张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此指理之源头而言无极故虚。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字。如天字。从此道字。而推上为本体。 由气化有道之名。此指生阴生阳之后。道之流行而言。中庸曰。率性之谓道。道字。如路字。从此道字而推去为用。 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此指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之后而言。虚者。理也。朱子曰。性是个有气质。方说得个性字。若人生而静以上。只说个天道。下性字不得。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指理虚气灵而言。朱子曰。横渠心统性情语。极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则恐不能无病。便似性外别有一个知觉了。 盖横渠此说。论性论气。总合而言。故与圣贤诸说似异。然朱子不收入于近思录。亦似有微意。
心是活物。若不操存。则易出入无定处。故孟子言此以诫人。范女不识其本意而讥之。心之本体。如明镜止水。故范女谓之心无出入。程子所谓此女。虽不识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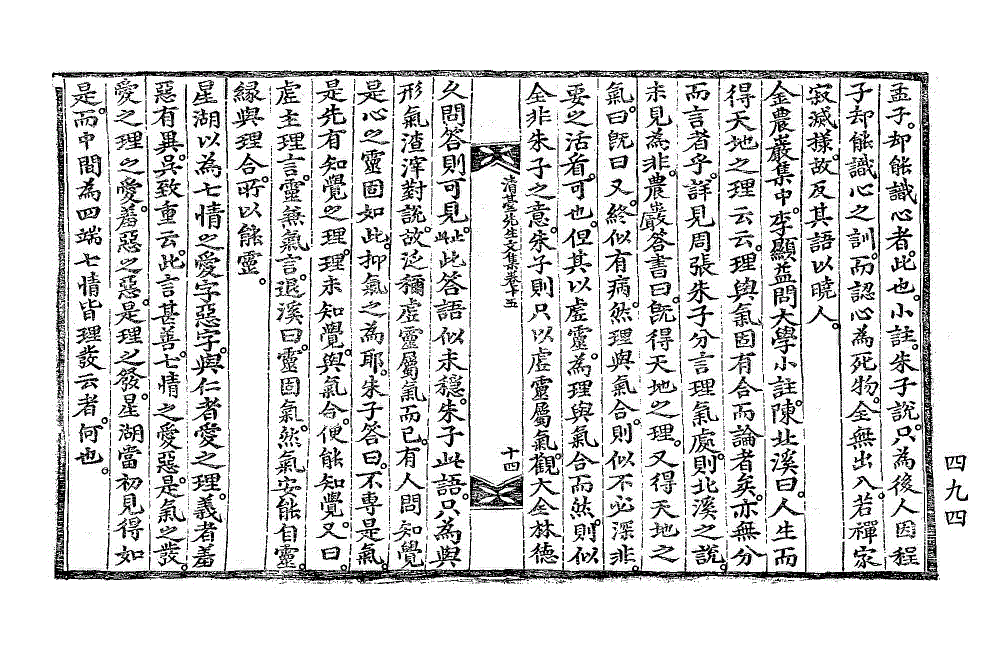 孟子。却能识心者。此也。小注。朱子说。只为后人因程子却能识心之训。而认心为死物。全无出入。若禅家寂灭㨾。故反其语以晓人。
孟子。却能识心者。此也。小注。朱子说。只为后人因程子却能识心之训。而认心为死物。全无出入。若禅家寂灭㨾。故反其语以晓人。金农岩集中。李显益问大学小注。陈北溪曰。人生而得天地之理云云。理与气固有合而论者矣。亦无分而言者乎。详见周张朱子分言理气处。则北溪之说。未见为非。农岩答书曰。既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气。曰既曰又。终似有病。然理与气合。则似不必深非。要之活看。可也。但其以虚灵。为理与气合而然。则似全非朱子之意。朱子则只以虚灵属气。观大全林德久问答则可见。(止此)此答语似未稳。朱子此语。只为与形气渣滓对说。故泛称虚灵属气而已。有人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朱子答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与气合。便能知觉。又曰。虚主理言。灵兼气言。退溪曰。灵固气。然气安能自灵。缘与理合。所以能灵。
星湖以为七情之爱字恶字。与仁者爱之理。义者羞恶有异。吴致重云。此言甚善。七情之爱恶。是气之发。爱之理之爱。羞恶之恶。是理之发。星湖当初见得如是。而中间为四端七情皆理发云者。何也。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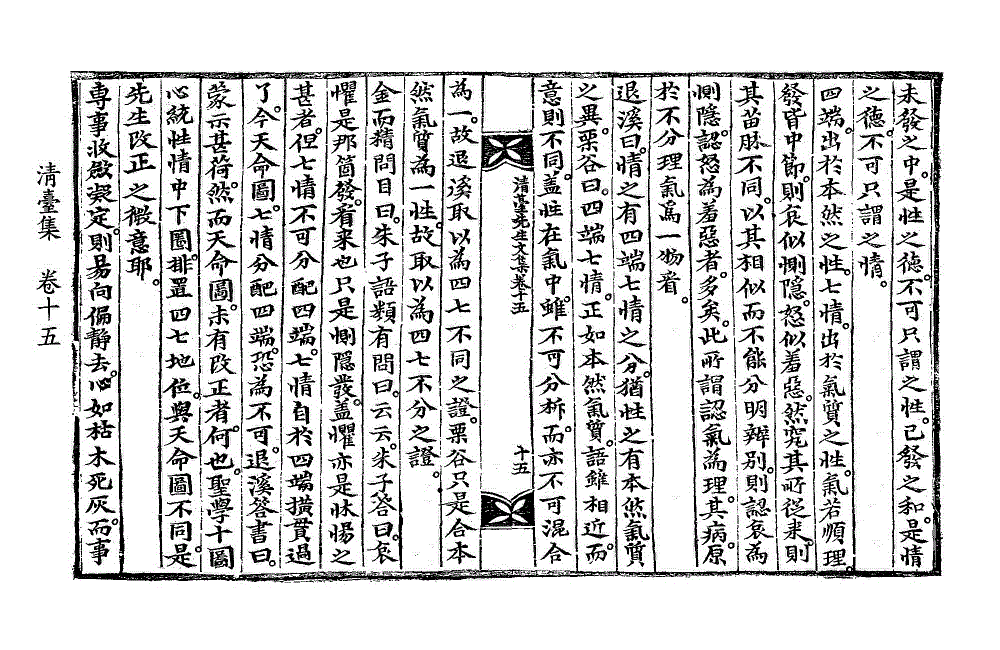 未发之中。是性之德。不可只谓之性。已发之和。是情之德。不可只谓之情。
未发之中。是性之德。不可只谓之性。已发之和。是情之德。不可只谓之情。四端。出于本然之性。七情。出于气质之性。气若顺理。发皆中节。则哀似恻隐。怒似羞恶。然究其所从来。则其苗脉不同。以其相似而不能分明辨别。则认哀为恻隐。认怒为羞恶者。多矣。此所谓认气为理。其病。原于不分理气为一物看。
退溪曰。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然气质之异。栗谷曰。四端七情。正如本然气质。语虽相近。而意则不同。盖性在气中。虽不可分析。而亦不可混合为一。故退溪取以为四七不同之證。栗谷只是合本然气质为一性。故取以为四七不分之證。
金而精问目曰。朱子语类有问曰。云云。朱子答曰。哀惧是那个发。看来也只是恻隐发。盖惧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今天命图。七情分配四端。恐为不可。退溪答书曰。蒙示甚荷。然而天命图。未有改正者。何也。圣学十图心统性情中下圈。排置四七地位。与天命图不同。是先生改正之微意耶。
专事收敛凝定。则易向偏静去。心如枯木死灰。而事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5L 页
 物之来。无以酬应。此最可畏。须于敬字上着力。而格致诚正两头齐进。则静中自有活底意思。于当应处必应。若于不当应而应者。心失于偏动。而不能主宰存养之病也。当应而不应者。心失于偏静。而不能主宰省察之病也。心无主宰。则当静处不静。如乱麻惊浪。靡有定处。当动处不动。如枯木死灰。小无生意。盖当静而不静。则亦当动而不动矣。
物之来。无以酬应。此最可畏。须于敬字上着力。而格致诚正两头齐进。则静中自有活底意思。于当应处必应。若于不当应而应者。心失于偏动。而不能主宰存养之病也。当应而不应者。心失于偏静。而不能主宰省察之病也。心无主宰。则当静处不静。如乱麻惊浪。靡有定处。当动处不动。如枯木死灰。小无生意。盖当静而不静。则亦当动而不动矣。养之义。如雨露之滋润草木。饮食之供奉口体。涵养此心于义理。如以物沉水。欲其久久浃洽。而内外通透。故贯动静而言。天理安静时。此心湛然于内。天理发用时。此心蔼然于外。则自然德厚而仁熟矣。
心既存养得久。则不待其省觉而能察善恶。然此非初学事。惟心念初发时。当察其公私义利之分数多寡。一存一去。日渐减一分长一分。则自然有进。
孟子求放心一款。今人多错认。以为别有他一心。照捡这一心。知其放失而求之。此与释氏以心观心之说同。不可不体验得。陈北溪曰。出非是里面本体。走出外去。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体。遂不见了云云。
圣贤许多说话。不过知行两字。学者一生工夫。都只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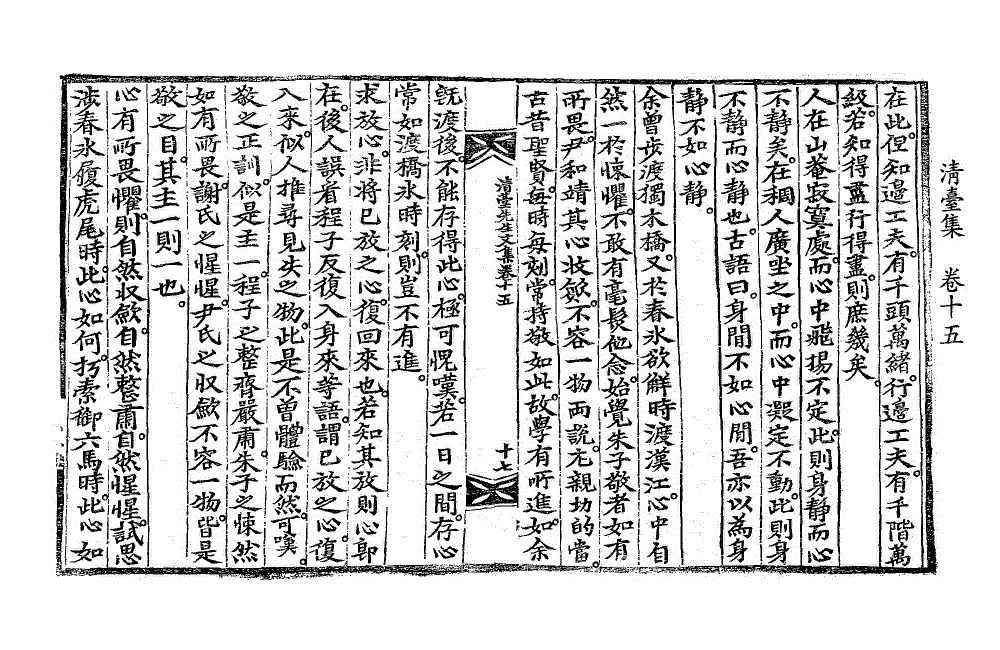 在此。但知边工夫。有千头万绪。行边工夫。有千阶万级。若知得尽行得尽。则庶几矣。
在此。但知边工夫。有千头万绪。行边工夫。有千阶万级。若知得尽行得尽。则庶几矣。人在山庵寂寞处。而心中飞扬不定。此则身静而心不静矣。在稠人广坐之中。而心中凝定不动。此则身不静而心静也。古语曰。身閒不如心閒。吾亦以为身静不如心静。
余曾步渡独木桥。又于春冰欲解时渡汉江。心中自然一于悚惧。不敢有毫发他念。始觉朱子敬者如有所畏。尹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两说。尤亲切的当。古昔圣贤。每时每刻。常持敬如此。故学有所进。如余既渡后。不能存得此心。极可愧叹。若一日之间。存心常如渡桥冰时刻。则岂不有进。
求放心。非将已放之心。复回来也。若知其放则心即在。后人误看程子反复入身来等语。谓已放之心。复入来。似人推寻见失之物。此是不曾体验而然。可叹。
敬之正训。似是主一。程子之整齐严肃。朱子之悚然如有所畏。谢氏之惺惺。尹氏之收敛不容一物。皆是敬之目。其主一则一也。
心有所畏惧。则自然收敛。自然整肃。自然惺惺。试思涉春冰履虎尾时。此心如何。朽索御六马时。此心如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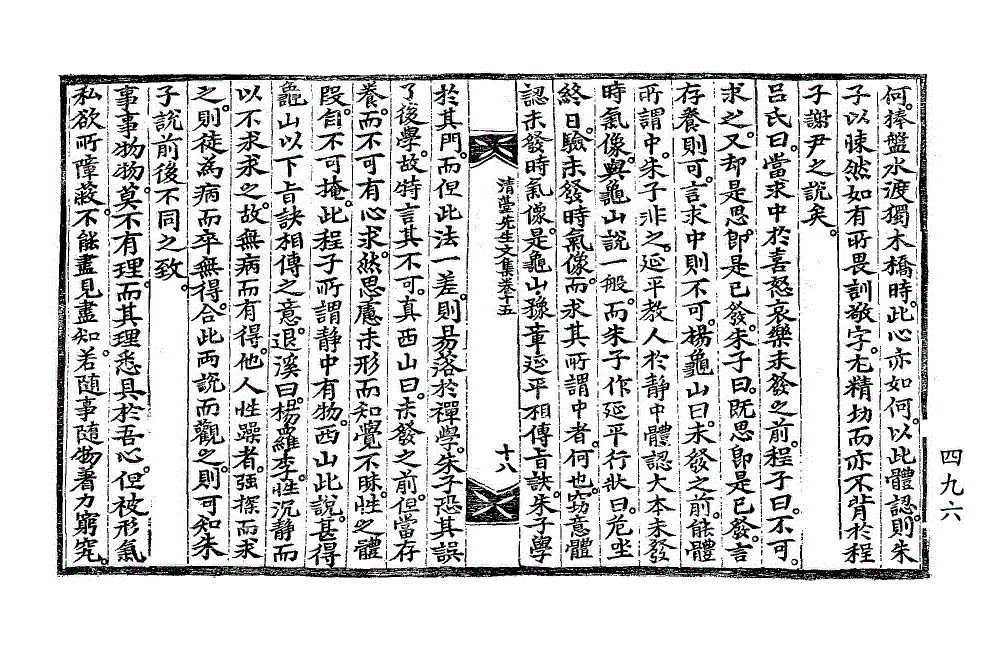 何。捧盘水渡独木桥时。此心亦如何。以此体认。则朱子以悚然如有所畏训敬字。尤精切而亦不背于程子谢尹之说矣。
何。捧盘水渡独木桥时。此心亦如何。以此体认。则朱子以悚然如有所畏训敬字。尤精切而亦不背于程子谢尹之说矣。吕氏曰。当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曰。不可。求之。又却是思。即是已发。朱子曰。既思即是已发。言存养则可。言求中则不可。杨龟山曰。未发之前。能体所谓中。朱子非之。延平教人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像。与龟山说一般。而朱子作延平行状曰。危坐终日。验未发时气像。而求其所谓中者。何也。窃意体认未发时气像。是龟山,豫章,延平相传旨诀。朱子学于其门。而但此法一差。则易落于禅学。朱子恐其误了后学。故特言其不可。真西山曰。未发之前。但当存养。而不可有心求。然思虑未形而知觉不昧。性之体段。自不可掩。此程子所谓静中有物。西山此说。甚得龟山以下旨诀相传之意。退溪曰。杨,罗,李。性沉静而以不求求之。故无病而有得。他人性躁者。强探而求之。则徒为病而卒无得。合此两说而观之。则可知朱子说前后不同之致。
事事物物。莫不有理。而其理悉具于吾心。但被形气私欲所障蔽。不能尽见尽知。若随事随物着力穷究。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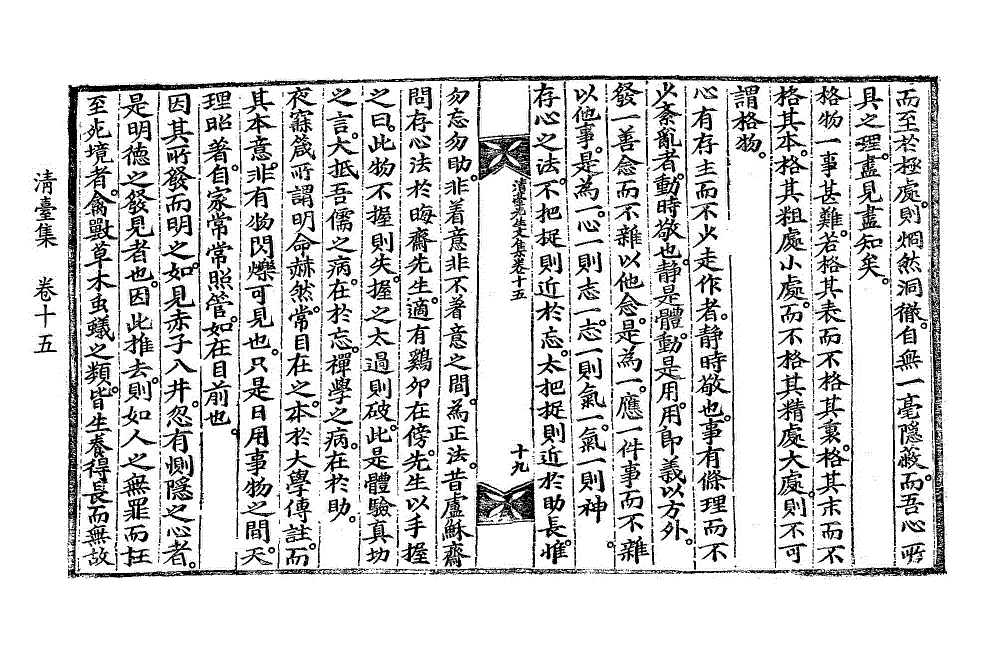 而至于极处。则烱然洞彻。自无一毫隐蔽。而吾心所具之理。尽见尽知矣。
而至于极处。则烱然洞彻。自无一毫隐蔽。而吾心所具之理。尽见尽知矣。格物一事甚难。若格其表而不格其里。格其末而不格其本。格其粗处小处。而不格其精处大处。则不可谓格物。
心有存主而不少走作者。静时敬也。事有条理而不少紊乱者。动时敬也。静是体。动是用。用即义以方外。
发一善念而不杂以他念。是为一。应一件事而不杂以他事。是为一。心一则志一。志一则气一。气一则神▣。
存心之法。不把捉则近于忘。太把捉则近于助长。惟勿忘勿助。非着意非不着意之间。为正法。昔卢稣斋问存心法于晦斋先生。适有鸡卵在傍。先生以手握之曰。此物不握则失。握之太过则破。此是体验真切之言。大抵吾儒之病。在于忘。禅学之病。在于助。
夜寐箴所谓明命赫然。常目在之。本于大学传注。而其本意。非有物闪烁可见也。只是日用事物之间。天理昭著。自家常常照管。如在目前也。
因其所发而明之。如见赤子入井。忽有恻隐之心者。是明德之发见者也。因此推去。则如人之无罪而枉至死境者。禽兽草木虫蚁之类。皆生养得长而无故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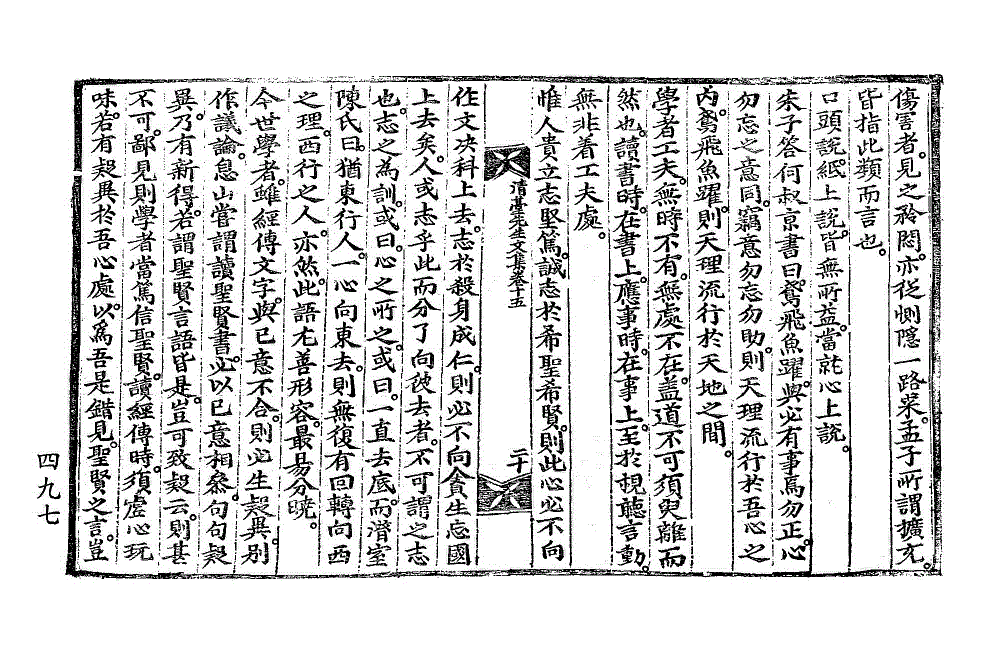 伤害者。见之矜闷。亦从恻隐一路来。孟子所谓扩充。皆指此类而言也。
伤害者。见之矜闷。亦从恻隐一路来。孟子所谓扩充。皆指此类而言也。口头说。纸上说。皆无所益。当就心上说。
朱子答何叔京书曰。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之意同。窃意勿忘勿助。则天理流行于吾心之内。鸢飞鱼跃。则天理流行于天地之间。
学者工夫。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盖道不可须臾离而然也。读书时。在书上。应事时。在事上。至于视听言动。无非着工夫处。
惟人贵立志坚笃。诚志于希圣希贤。则此心必不向作文决科上去。志于杀身成仁。则必不向贪生忘国上去矣。人或志乎此而分了向彼去者。不可谓之志也。志之为训。或曰。心之所之。或曰。一直去底。而潜室陈氏曰。犹东行人。一心向东去。则无复有回转向西之理。西行之人。亦然。此语尤善形容。最易分晓。
今世学者。虽经传文字。与己意不合。则必生疑异。别作议论。息山尝谓读圣贤书。必以己意相参。句句疑异。乃有新得。若谓圣贤言语皆是。岂可致疑云。则甚不可。鄙见则学者当笃信圣贤。读经传时。须虚心玩味。若有疑异于吾心处。以为吾是错见。圣贤之言。岂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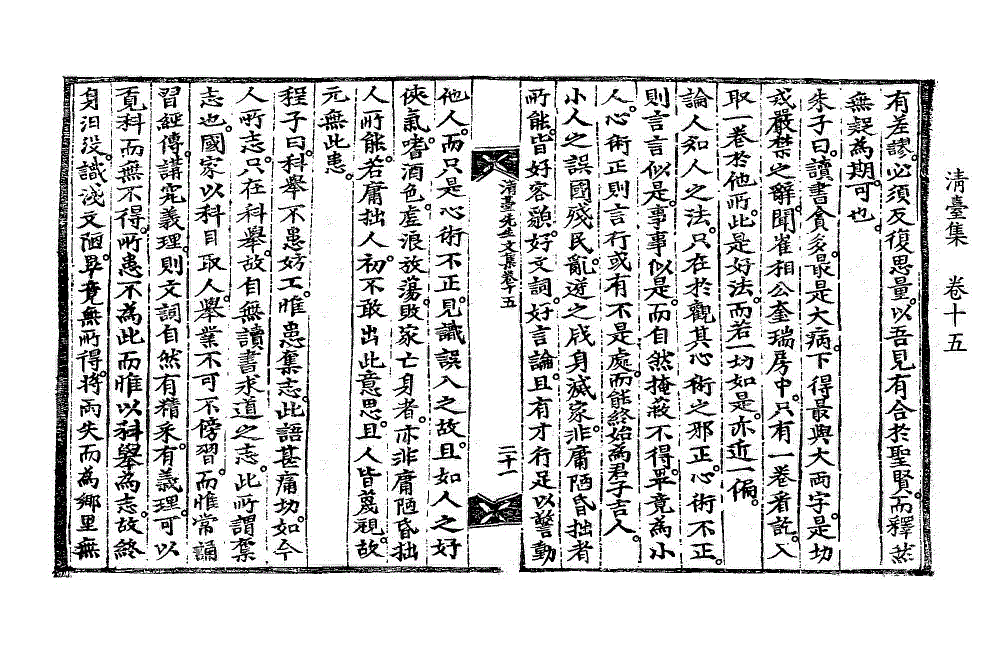 有差谬。必须反复思量。以吾见有合于圣贤。而释然无疑为期。可也。
有差谬。必须反复思量。以吾见有合于圣贤。而释然无疑为期。可也。朱子曰。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得最与大两字。是切戒严禁之辞。闻崔相公奎瑞房中。只有一卷看讫。又取一卷于他所。此是好法。而若一切如是。亦近一偏。
论人知人之法。只在于观其心术之邪正。心术不正。则言言似是。事事似是。而自然掩蔽不得。毕竟为小人。心术正则言行或有不是处。而能终始为君子吉人。
小人之误国残民。乱逆之戕身灭家。非庸陋昏拙者所能。皆好容貌。好文词。好言论。且有才行足以警动他人。而只是心术不正。见识误入之故。且如人之好侠气。嗜酒色。虚浪放荡。败家亡身者。亦非庸陋昏拙人所能。若庸拙人。初不敢出此意思。且人皆蔑视。故元无此患。
程子曰。科举不患妨工。惟患夺志。此语甚痛切。如今人所志。只在科举。故自无读书求道之志。此所谓夺志也。国家以科目取人。举业不可不傍习。而惟常诵习经传。讲究义理。则文词自然有精采。有义理。可以觅科而无不得。所患不为此而惟以科举为志。故终身汩没。识浅文陋。毕竟无所得。将两失而为乡里无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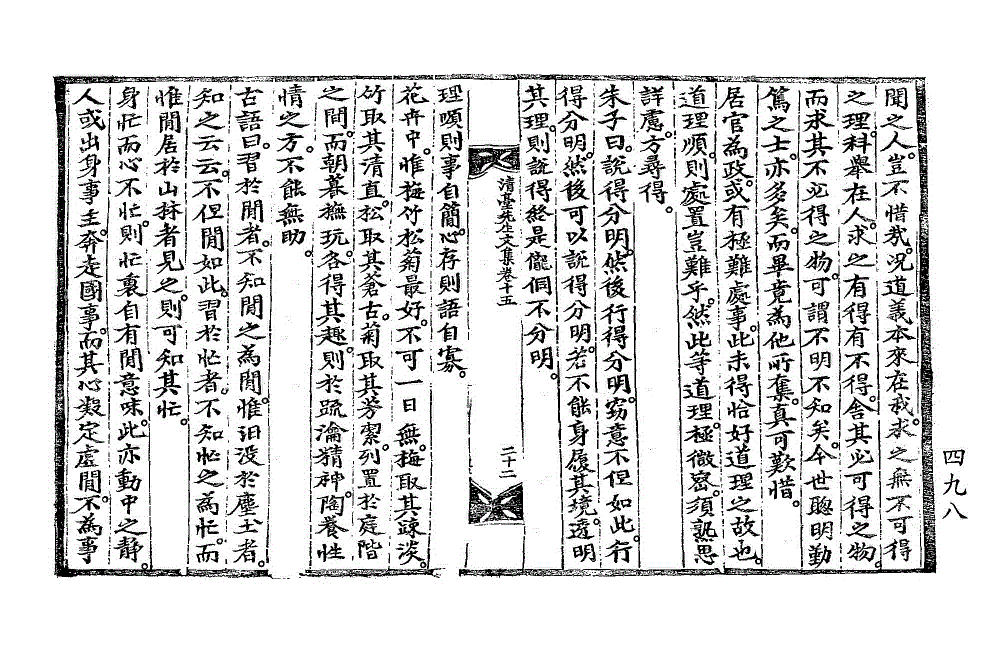 闻之人。岂不惜哉。况道义本来在我。求之无不可得之理。科举在人。求之有得有不得。舍其必可得之物。而求其不必得之物。可谓不明不知矣。今世聪明勤笃之士。亦多矣。而毕竟为他所夺。真可叹惜。
闻之人。岂不惜哉。况道义本来在我。求之无不可得之理。科举在人。求之有得有不得。舍其必可得之物。而求其不必得之物。可谓不明不知矣。今世聪明勤笃之士。亦多矣。而毕竟为他所夺。真可叹惜。居官为政。或有极难处事。此未得恰好道理之故也。道理顺。则处置岂难乎。然此等道理。极微密。须熟思详虑。方寻得。
朱子曰。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窃意不但如此。行得分明。然后可以说得分明。若不能身履其境。透明其理。则说得终是儱侗不分明。
理顺则事自𢂴。心存则语自寡。
花卉中。惟梅竹松菊最好。不可一日无。梅取其疏淡。竹取其清直。松取其苍古。菊取其芳洁。列置于庭阶之间。而朝暮抚玩。各得其趣。则于疏瀹精神。陶养性情之方。不能无助。
古语曰。习于閒者。不知閒之为閒。惟汩没于尘土者。知之云云。不但閒如此。习于忙者。不知忙之为忙。而惟閒居于山林者见之。则可知其忙。
身忙而心不忙。则忙里自有閒意味。此亦动中之静。人或出身事主。奔走国事。而其心凝定虚閒。不为事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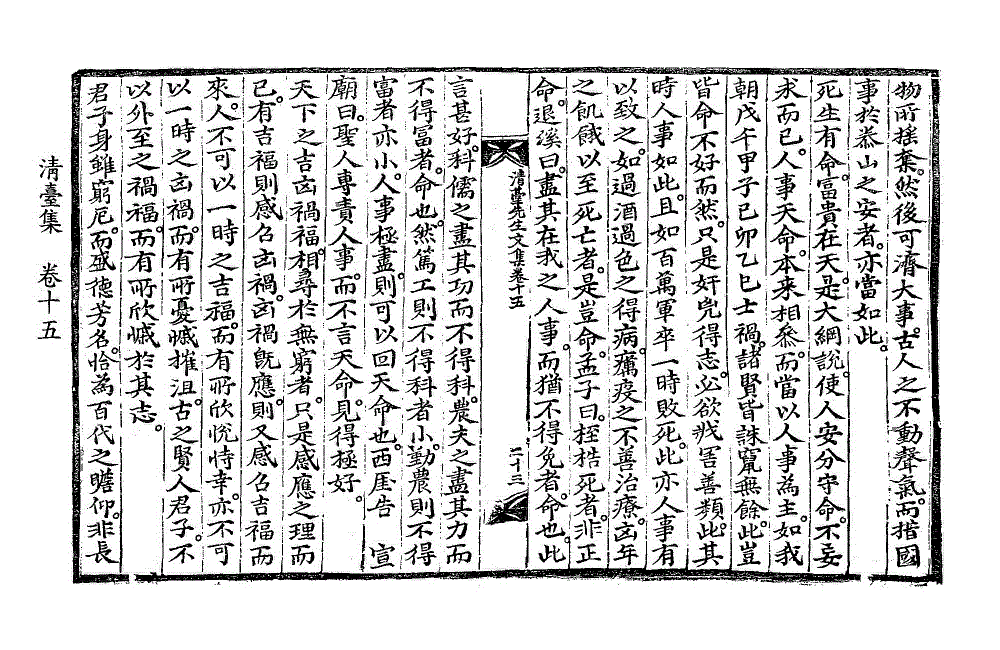 物所摇夺。然后可济大事。古人之不动声气。而措国事于泰山之安者。亦当如此。
物所摇夺。然后可济大事。古人之不动声气。而措国事于泰山之安者。亦当如此。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大纲说。使人安分守命。不妄求而已。人事天命。本来相参。而当以人事为主。如我朝戊午甲子己卯乙巳士祸。诸贤皆诛窜无馀。此岂皆命不好而然。只是奸凶得志。必欲戕害善类。此其时人事如此。且如百万军卒一时败死。此亦人事有以致之。如过酒过色之得病。疠疫之不善治疗。凶年之饥饿以至死亡者。是岂命。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退溪曰。尽其在我之人事。而犹不得免者。命也。此言甚好。科儒之尽其功而不得科。农夫之尽其力而不得富者。命也。然笃工则不得科者小。勤农则不得富者亦小。人事极尽。则可以回天命也。西厓告 宣庙曰。圣人专责人事。而不言天命。见得极好。
天下之吉凶祸福。相寻于无穷者。只是感应之理而已。有吉福则感召凶祸。凶祸既应。则又感召吉福而来。人不可以一时之吉福。而有所欣悦恃幸。亦不可以一时之凶祸。而有所忧戚摧沮。古之贤人君子。不以外至之祸福。而有所欣戚于其志。
君子身虽穷厄。而盛德芳名。恰为百代之瞻仰。非长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499L 页
 不幸也。乃长幸也。小人身虽安乐。而奸状谀态。不免后人之诛贬。则非长幸也。乃长不幸也。
不幸也。乃长幸也。小人身虽安乐。而奸状谀态。不免后人之诛贬。则非长幸也。乃长不幸也。平是至正至中底道理。不高不低而后。衡得其平。无过不及而后。事得其平。是天地自然之理。似易而极难。似卑而极高。故乐声。羽调则易。而平调则难。诗与文。险奇雄丽则易。而平淡则难。此不可学而能。亦不可勉强而能。惟其心气平正冲淡。然后自然如此。
宋张文节曰。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止此)盖言理势之必至。而其言切中后弊。余见近世卿宰家。俸禄优入时。不能俭约。祭祀婚丧及衣服饮食。极其礼足华美。子孙自幼少时。习见其如此。及俸禄绝而犹不敢变改。逐岁卖田卖奴婢以供之。不久田奴俱尽。流离失所。全失门户者甚多。良可恻悯。偶见文节此语。不觉心有所感。书以为戒。
山家风水之说。如程朱子两说。加减不得。今俗专以子孙祸福贫贱富贵及后裔之多寡。皆归于祖先葬地。极可叹闷。且为地师妖说所动。迁移久远坟墓。遭祸败者甚多。盖神道尚静。迁动则生祸固然矣。风水之说。当置之可信不可信之间。子孙祸福。专归于冢中枯骨。其理杳茫。当择山水回抱。藏风向阳处葬亲。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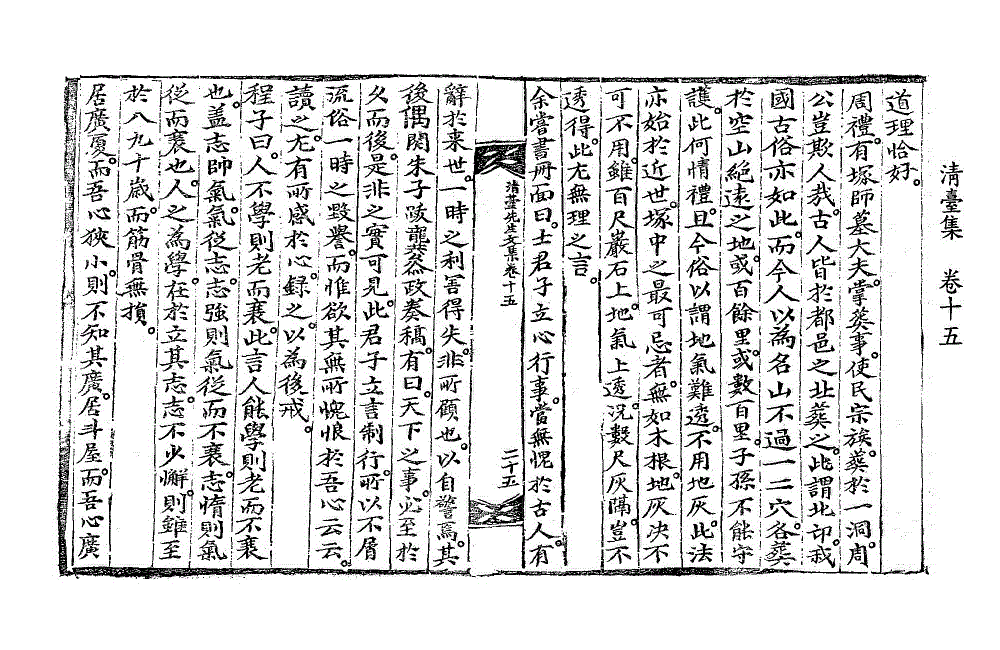 道理恰好。
道理恰好。周礼。有冢师墓大夫。掌葬事。使民宗族。葬于一洞。周公岂欺人哉。古人皆于都邑之北葬之。此谓北邙。我国古俗亦如此。而今人以为名山不过一二穴。各葬于空山绝远之地。或百馀里。或数百里。子孙不能守护。此何情礼。且今俗以谓地气难透。不用地灰。此法亦始于近世。冢中之最可忌者。无如木根。地灰决不可不用。虽百尺岩石上。地气上透。况数尺灰隔。岂不透得。此尤无理之言。
余尝书册面曰。士君子立心行事。当无愧于古人。有辞于来世。一时之利害得失。非所顾也。以自警焉。其后偶阅朱子跋龚参政奏稿。有曰。天下之事。必至于久而后。是非之实可见。此君子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时之毁誉。而惟欲其无所愧恨于吾心云云。读之。尤有所感于心。录之。以为后戒。
程子曰。人不学则老而衰。此言人能学则老而不衰也。盖志帅气。气从志。志强则气从而不衰。志惰则气从而衰也。人之为学。在于立其志。志不少懈。则虽至于八九十岁。而筋骨无损。
居广厦。而吾心狭小。则不知其广。居斗屋。而吾心广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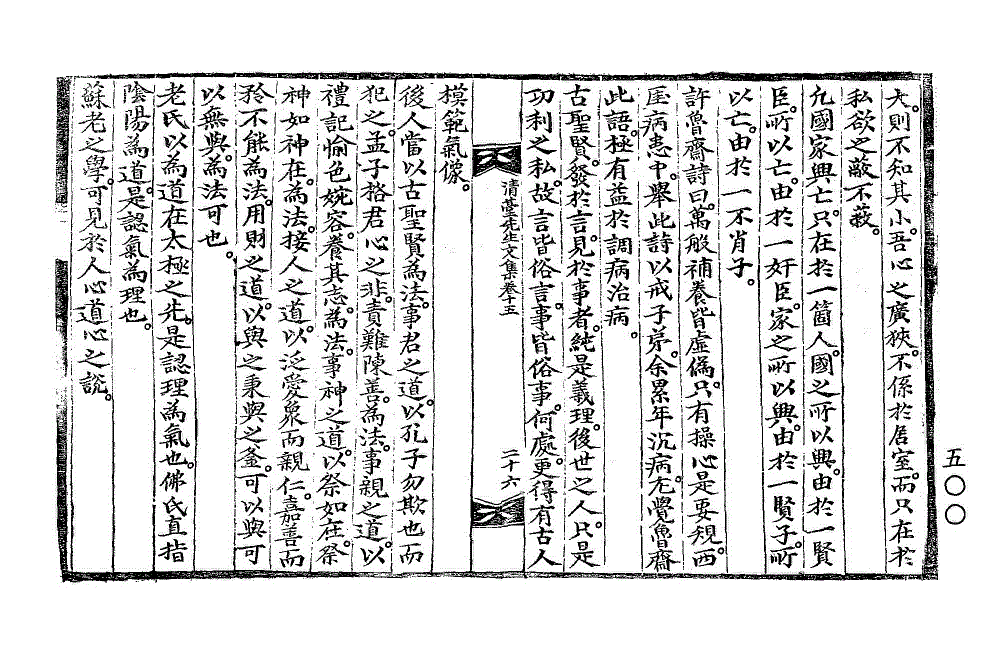 大。则不知其小。吾心之广狭。不系于居室。而只在于私欲之蔽不蔽。
大。则不知其小。吾心之广狭。不系于居室。而只在于私欲之蔽不蔽。凡国家兴亡。只在于一个人。国之所以兴。由于一贤臣。所以亡。由于一奸臣。家之所以兴。由于一贤子。所以亡。由于一不肖子。
许鲁斋诗曰。万般补养皆虚伪。只有操心是要规。西厓病患中。举此诗以戒子弟。余累年沉病。尤觉鲁斋此语。极有益于调病治病。
古圣贤。发于言。见于事者。纯是义理。后世之人。只是功利之私。故言皆俗言。事皆俗事。何处。更得有古人模范气像。
后人当以古圣贤为法。事君之道。以孔子勿欺也而犯之。孟子格君心之非。责难陈善。为法。事亲之道。以礼记愉色婉容。养其志。为法。事神之道。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为法。接人之道。以泛爱众而亲仁。嘉善而矜不能为法。用财之道。以与之秉与之釜。可以与可以无与。为法可也。
老氏以为道在太极之先。是认理为气也。佛氏直指阴阳为道。是认气为理也。
苏老之学。可见于人心道心之说。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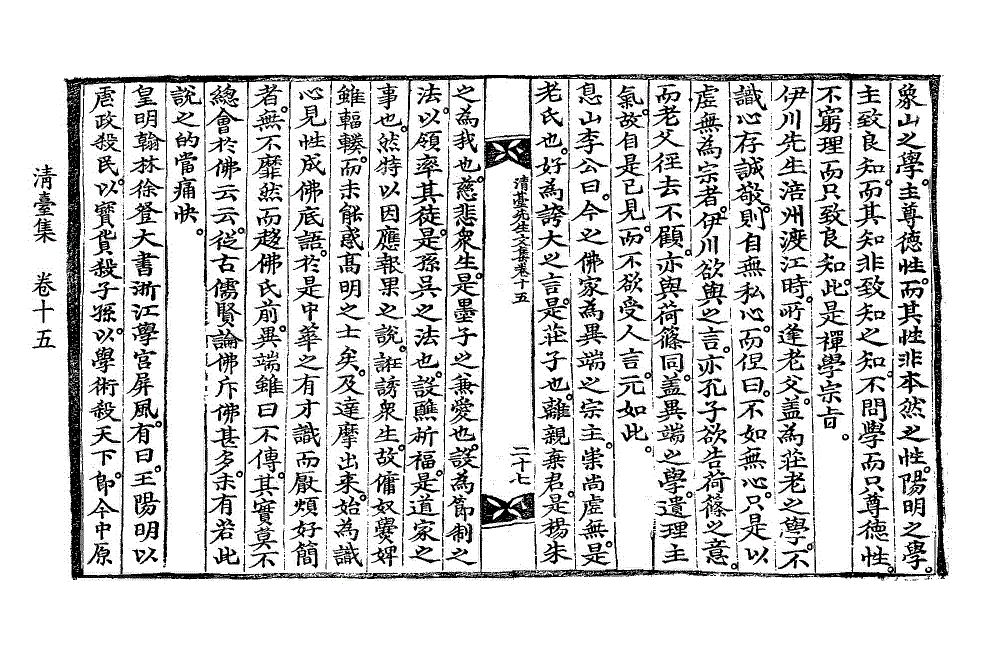 象山之学。主尊德性。而其性非本然之性。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其知非致知之知。不问学而只尊德性。不穷理而只致良知。此是禅学宗旨。
象山之学。主尊德性。而其性非本然之性。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其知非致知之知。不问学而只尊德性。不穷理而只致良知。此是禅学宗旨。伊川先生涪州渡江时。所逢老父。盖为庄老之学。不识心存诚敬。则自无私心。而但曰。不如无心。只是以虚无为宗者。伊川欲与之言。亦孔子欲告荷筱之意。而老父径去不顾。亦与荷筱同。盖异端之学。遗理主气。故自是己见。而不欲受人言。元如此。
息山李公曰。今之佛家为异端之宗主。崇尚虚无。是老氏也。好为誇大之言。是庄子也。离亲弃君。是杨朱之为我也。慈悲众生。是墨子之兼爱也。设为节制之法。以领率其徒。是孙吴之法也。设醮祈福。是道家之事也。然特以因应报果之说。诳诱众生。故佣奴爨婢虽辐辏。而未能惑高明之士矣。及达摩出来。始为识心见性成佛底语。于是中华之有才识而厌烦好简者。无不靡然而趍佛氏前。异端虽曰不传。其实莫不总会于佛云云。从古儒贤论佛斥佛甚多。未有若此说之的当痛快。
皇明翰林徐登大书浙江学宫屏风。有曰。王阳明以虐政杀民。以宝货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即今中原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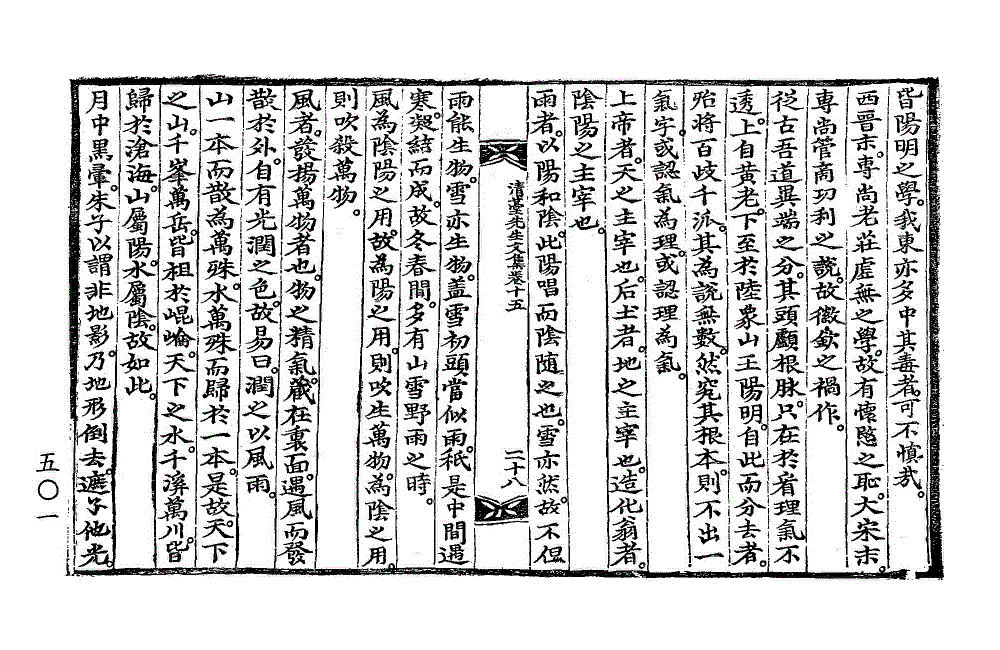 皆阳明之学。我东亦多中其毒者。可不慎哉。
皆阳明之学。我东亦多中其毒者。可不慎哉。西晋末。专尚老庄虚无之学。故有怀悯之耻。大宋末。专尚管商功利之说。故徽,钦之祸作。
从古吾道异端之分。其头颅根脉。只在于看理气不透。上自黄老。下至于陆象山王阳明。自此而分去者。殆将百歧千派。其为说无数。然究其根本。则不出一气字。或认气为理。或认理为气。
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后土者。地之主宰也。造化翁者。阴阳之主宰也。
雨者。以阳和阴。此阳唱而阴随之也。雪亦然。故不但雨能生物。雪亦生物。盖雪初头当似雨。秖是中间遇寒。凝结而成。故冬春间。多有山雪野雨之时。
风为阴阳之用。故为阳之用。则吹生万物。为阴之用。则吹杀万物。
风者。发扬万物者也。物之精气。藏在里面。遇风而发散于外。自有光润之色。故易曰。润之以风雨。
山一本而散为万殊。水万殊而归于一本。是故。天下之山。千峰万岳。皆祖于昆崙。天下之水。千溪万川。皆归于沧海。山属阳。水属阴。故如此。
月中黑晕。朱子以谓非地影。乃地形倒去。遮了他光。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2H 页
 如镜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李息山以为阴气凝聚不散之处。盖月是阴魄。日光被地遮不尽照。则其不照处。阴魄依旧自在无光。
如镜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李息山以为阴气凝聚不散之处。盖月是阴魄。日光被地遮不尽照。则其不照处。阴魄依旧自在无光。古人以露为星月之气。汉武帝承露盘。是欲食星月之气以延年也。至朱子。始言露是地气蒸上。盖露是阳液也。阳气从地上升而成露。自白露至寒露。自寒露至霜降。霜是阴液也。阳变为阴。故露结为霜。
近一远三。言分天体为四。如十二方位。卯辰巳为一位。午未申为二位。酉戌亥为三位。子丑寅为四位。晦日则日月相会。自初一日渐离。至初九日。则日月相距。其间近一分而远三分。所近者。子丑寅一方也。所远者。卯辰巳至酉戌亥三方也。舒前缩后者。始卯辰至戌亥为前。其间甚远故舒也。子丑寅为后。其间甚近故缩也。
曾见性理大全。程子曰。长安西风而雨。此理不可晓云。余寓山庵时。见东风来触于西峰。转去不得。因反向东边去。见林叶可知。因思长安之西风亦如此。盖长安三面皆峻岭。惟东一面稍通。故天欲雨。则风自东向西而触于峻岭。不得转去。其势不得不反向于东而散。故人作西风看。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2L 页
 虹者。天地之淫气。淫者。过也。阴阳之正气合和则为雨。其淫气合和则为虹。故虹有雌雄。必于雨晴时见者。和合之馀也。色有青红白者。五行之气。而白是金气。故白虹为兵象。三月始见。十月始藏者。阴阳交与不交之时也。或有白虹贯月之时。此非虹也。阴气太盛。四面傍出。而如虹如晕。贯月之中而围匝于外也。十月后见者。阴阳之失其常而然也。或曰螮蝀。或曰虹蜺。皆变化为物形之故也。故字皆从虫。霖雨时。不见。而必见于急雨后者。霖雨时阴阳之和合从容。故无淫气。急雨时和合甚急。故其气淫而为虹。
虹者。天地之淫气。淫者。过也。阴阳之正气合和则为雨。其淫气合和则为虹。故虹有雌雄。必于雨晴时见者。和合之馀也。色有青红白者。五行之气。而白是金气。故白虹为兵象。三月始见。十月始藏者。阴阳交与不交之时也。或有白虹贯月之时。此非虹也。阴气太盛。四面傍出。而如虹如晕。贯月之中而围匝于外也。十月后见者。阴阳之失其常而然也。或曰螮蝀。或曰虹蜺。皆变化为物形之故也。故字皆从虫。霖雨时。不见。而必见于急雨后者。霖雨时阴阳之和合从容。故无淫气。急雨时和合甚急。故其气淫而为虹。冬至后。有大小寒者。阳在里面渐长。故推出阴气于外故也。夏至后。大小暑亦然。
天地之间。只是感应之理而已。天气感召地气而上升。地气感召天气而下降。
天虽空虚。而实理充塞。是虚而实也。地虽坚实。而天气下透。是实而虚也。
息翁曰。梅花之冬开。是今年之气。而非明年之气。与秋菊冬柏同。此说似不然。梅花。自是先春之物。故得新春之气而即发也。秋菊冬柏。晚得今年之气。故春不花而秋冬始花也。庾岭梅则南方地暖。故腊月而开。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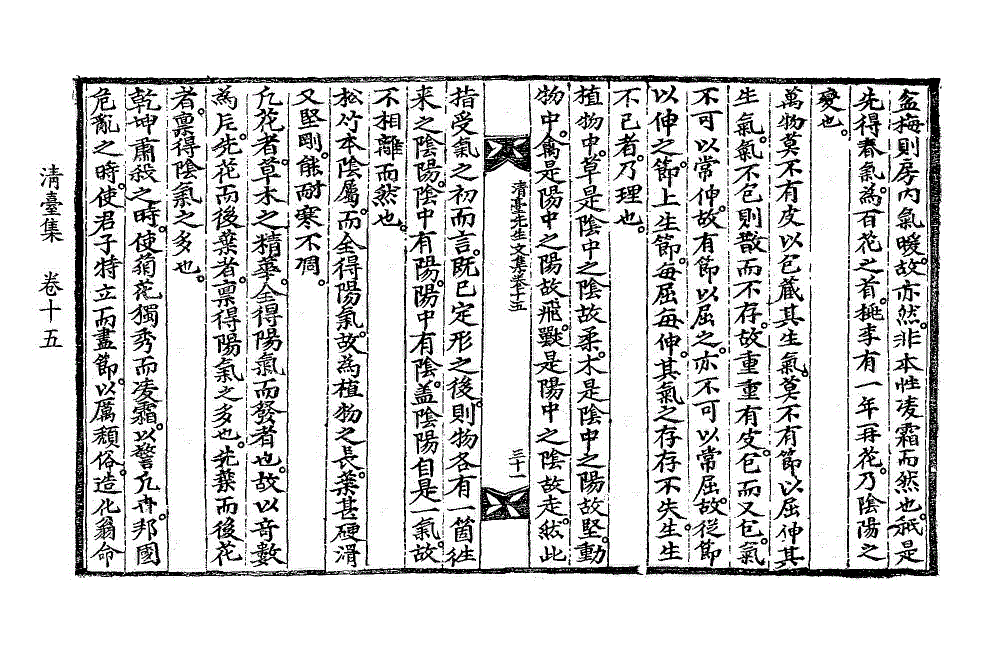 盆梅则房内气暖。故亦然。非本性凌霜而然也。秖是先得春气。为百花之首。桃李有一年再花。乃阴阳之变也。
盆梅则房内气暖。故亦然。非本性凌霜而然也。秖是先得春气。为百花之首。桃李有一年再花。乃阴阳之变也。万物莫不有皮以包藏其生气。莫不有节以屈伸其生气。气不包则散而不存。故重重有皮。包而又包。气不可以常伸。故有节以屈之。亦不可以常屈。故从节以伸之。节上生节。每屈每伸。其气之存存不失。生生不已者。乃理也。
植物中。草是阴中之阴故柔。木是阴中之阳故坚。动物中。禽是阳中之阳故飞。兽是阳中之阴故走。然此指受气之初而言。既已定形之后。则物各有一个往来之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盖阴阳自是一气。故不相离而然也。
松竹本阴属。而全得阳气。故为植物之长。叶甚硬滑又坚刚。能耐寒不凋。
凡花者。草木之精华。全得阳气而发者也。故以奇数为片。先花而后叶者。禀得阳气之多也。先叶而后花者。禀得阴气之多也。
乾坤肃杀之时。使菊花独秀而凌霜。以警凡世。邦国危乱之时。使君子特立而尽节。以厉颓俗。造化翁命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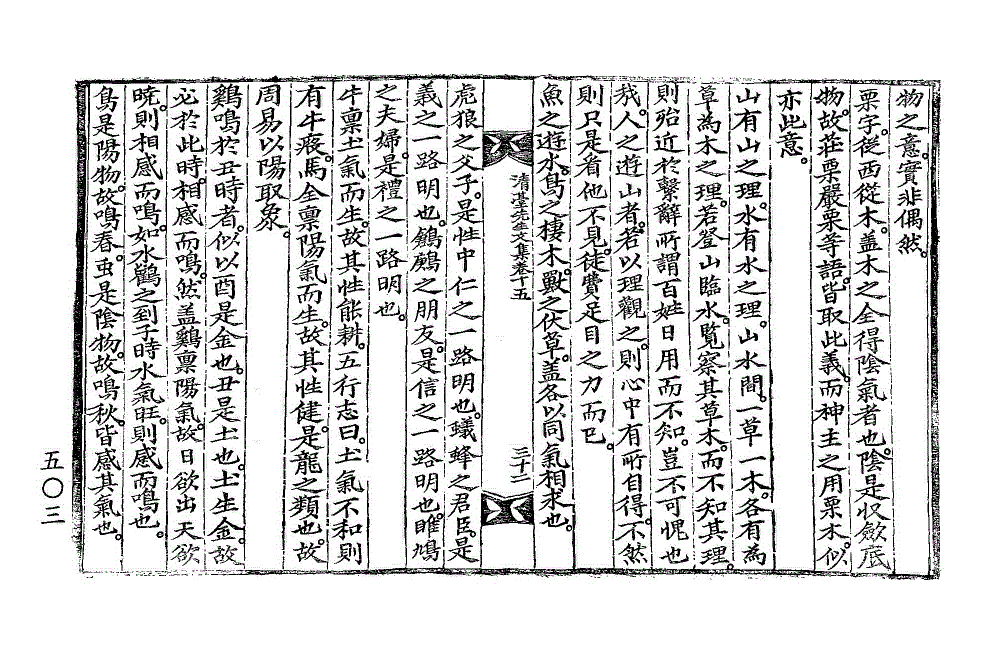 物之意。实非偶然。
物之意。实非偶然。栗字。从西从木。盖木之全得阴气者也。阴是收敛底物。故庄栗严栗等语。皆取此义。而神主之用栗木。似亦此意。
山有山之理。水有水之理。山水间。一草一木。各有为草为木之理。若登山临水。览察其草木。而不知其理。则殆近于系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岂不可愧也哉。人之游山者。若以理观之。则心中有所自得。不然则只是看他不见。徒费足目之力而已。
鱼之游水。鸟之栖木。兽之伏草。盖各以同气相求也。
虎狼之父子。是性中仁之一路明也。蚁蜂之君臣。是义之一路明也。鸧鹒之朋友。是信之一路明也。雎鸠之夫妇。是礼之一路明也。
牛禀土气而生。故其性能耕。五行志曰。土气不和则有牛疫。马全禀阳气而生。故其性健。是龙之类也。故周易以阳取象。
鸡鸣于丑时者。似以酉是金也。丑是土也。土生金。故必于此时。相感而鸣。然盖鸡禀阳气。故日欲出天欲晓。则相感而鸣。如水鹳之到子时水气旺。则感而鸣也。
鸟是阳物。故鸣春。虫是阴物。故鸣秋。皆感其气也。
清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5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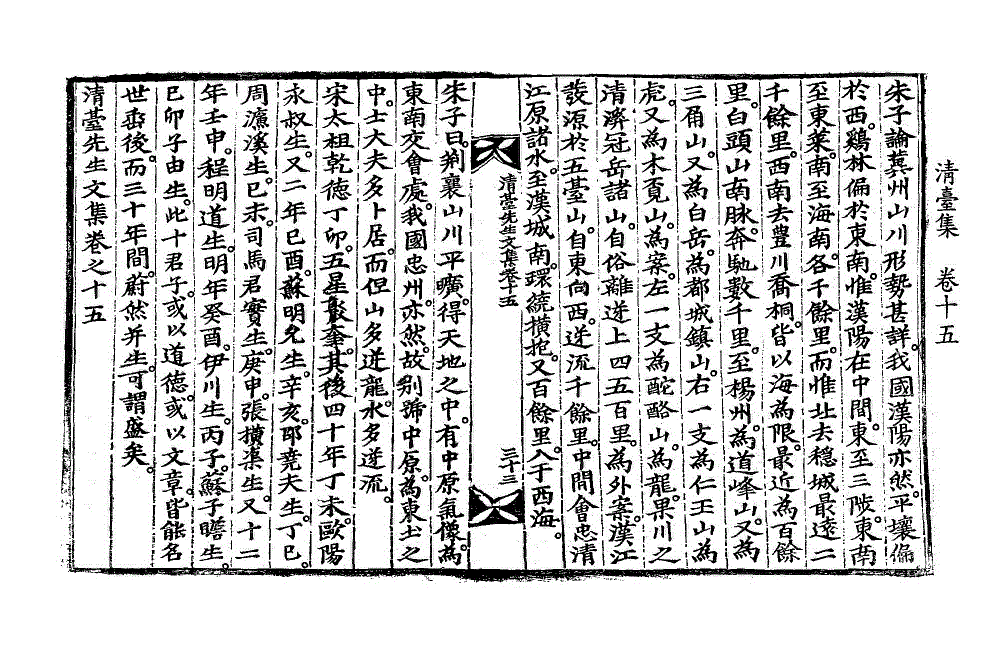 朱子论冀州山川形势甚详。我国汉阳亦然。平壤偏于西。鸡林偏于东南。惟汉阳在中间。东至三陟。东南至东莱。南至海南。各千馀里。而惟北去稳城最远二千馀里。西南去礼川乔桐。皆以海为限。最近为百馀里。白头山南脉。奔驰数千里。至杨州。为道峰山。又为三角山。又为白岳。为都城镇山。右一支为仁王山为虎。又为木觅山。为案。左一支为酡酪山。为龙。果川之清溪冠岳诸山。自俗离逆上四五百里。为外案。汉江发源于五台山。自东向西。逆流千馀里。中间会忠清江原诸水。至汉城南。环绕横抱。又百馀里。入于西海。
朱子论冀州山川形势甚详。我国汉阳亦然。平壤偏于西。鸡林偏于东南。惟汉阳在中间。东至三陟。东南至东莱。南至海南。各千馀里。而惟北去稳城最远二千馀里。西南去礼川乔桐。皆以海为限。最近为百馀里。白头山南脉。奔驰数千里。至杨州。为道峰山。又为三角山。又为白岳。为都城镇山。右一支为仁王山为虎。又为木觅山。为案。左一支为酡酪山。为龙。果川之清溪冠岳诸山。自俗离逆上四五百里。为外案。汉江发源于五台山。自东向西。逆流千馀里。中间会忠清江原诸水。至汉城南。环绕横抱。又百馀里。入于西海。朱子曰。荆襄山川平旷。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像。为东南交会处。我国忠州。亦然。故别号中原。为东土之中。士大夫多卜居。而但山多逆龙。水多逆流。
宋太祖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其后四十年丁未。欧阳永叔生。又二年己酉。苏明允生。辛亥。邵尧夫生。丁巳。周濂溪生。己未。司马君实生。庚申。张横渠生。又十二年壬申。程明道生。明年癸酉。伊川生。丙子。苏子瞻生。己卯子由生。此十君子。或以道德。或以文章。皆能名世垂后。而三十年间。蔚然并生。可谓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