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x 页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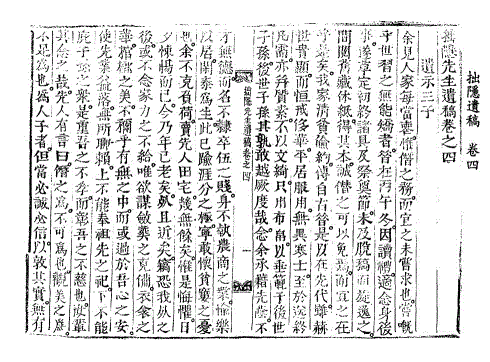 遗示三子
遗示三子余见人家每当丧。惟僭之务。而宜之未尝求也。尝嘅乎世习之无能矫者。昔在丙午冬。因读礼。适念身后事。遂草定初终诸具及祭奠节。未及脱稿而旋逸之。间阅旧藏休纸。得其本。诚僭之可以免焉。而宜之在乎是矣。我家清贫俭约。传自古昔。是以在先代。虽赫世贵显。而恒戒侈华。平居服用。无异寒士。至于送终凡需。亦并质素。不以文绮。只用布帛。以垂范于后世子孙。后世子孙其孰敢越厥度哉。念余承藉先荫。不才无德。而名不隶卒伍之贱。身不执农商之业。愉乐以居。闲泰为生。此已踰涯分之极。宁敢怀贫窭之忧也。余不克负荷。卖先人田宅。几无馀矣。惟是悔惧。日夕悚惕而已。今乃年已老矣。死且近矣。窃恐我死之后。或不念家力之不给。唯欲谋敛葬之克备。衣衾之华。棺椁之美。不称乎有无之中。而或过于吾心之安。使先业益落。无所聊赖。上不能奉祖先之祀。下不能庇子孙之众。是重吾之不孝。而彰吾之不慈也。汝辈其念之哉。先人有言曰。僭之为。不可为也。观美之为。不足为也。为人子者。但当必诚必信。以敦其实。无有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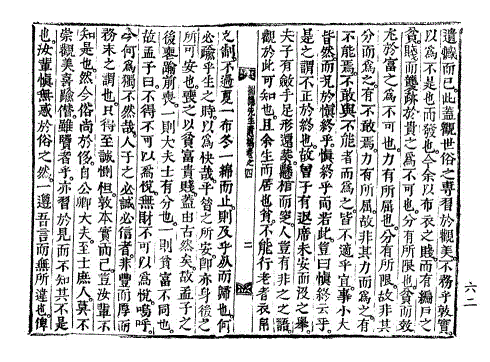 遗憾而已。此盖观世俗之专习于观美。不务乎敦实。以为不是也而发也。今余以布衣之贱。而有编户之贫。贱而袭迹于贵之为不可也。分有所限也。贫而效尤于当之为不可也。力有所屈也。分有所限。故非其分而为之。有不敢焉。力有所屈。故非其力而为之。有不能焉。不敢与不能者而为之。皆不适乎宜。事小大皆然。而况于慎终乎。慎终乎而若此。岂曰慎终云乎。是之谓不正于终也。故曾子有返席未安而没之举。夫子有敛手足形还葬。悬棺而窆。人岂有非之之语。观于此可知也。且余生而居也贫。不能行老者衣帛之制。不过夏一布冬一绵而止。则及乎死而归也。何必踰乎生之时。以为快哉。平昔之所安。即亦身后之所可安也。丧之以贫富贵贱。盖由古然矣。故孟子之后丧踰前丧。一则大夫士有分也。一则贫富不同也。故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呜呼。今何为独不然哉。人子之必诚必信者。非丰而厚而务末之谓也。只得至诚恻怛。敦本实而已。岂汝辈不知是也。然今俗尚于侈。自公卿大夫。至士庶人。莫不崇观美喜踰僭。虽贤者乎。亦习于见而不知其不是也。汝辈慎无惑于俗之然。一遵吾言而无所违也。俾
遗憾而已。此盖观世俗之专习于观美。不务乎敦实。以为不是也而发也。今余以布衣之贱。而有编户之贫。贱而袭迹于贵之为不可也。分有所限也。贫而效尤于当之为不可也。力有所屈也。分有所限。故非其分而为之。有不敢焉。力有所屈。故非其力而为之。有不能焉。不敢与不能者而为之。皆不适乎宜。事小大皆然。而况于慎终乎。慎终乎而若此。岂曰慎终云乎。是之谓不正于终也。故曾子有返席未安而没之举。夫子有敛手足形还葬。悬棺而窆。人岂有非之之语。观于此可知也。且余生而居也贫。不能行老者衣帛之制。不过夏一布冬一绵而止。则及乎死而归也。何必踰乎生之时。以为快哉。平昔之所安。即亦身后之所可安也。丧之以贫富贵贱。盖由古然矣。故孟子之后丧踰前丧。一则大夫士有分也。一则贫富不同也。故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呜呼。今何为独不然哉。人子之必诚必信者。非丰而厚而务末之谓也。只得至诚恻怛。敦本实而已。岂汝辈不知是也。然今俗尚于侈。自公卿大夫。至士庶人。莫不崇观美喜踰僭。虽贤者乎。亦习于见而不知其不是也。汝辈慎无惑于俗之然。一遵吾言而无所违也。俾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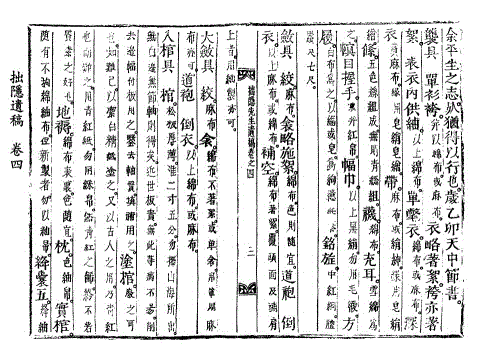 余平生之志。死犹得以行也。岁乙卯天中节书。
余平生之志。死犹得以行也。岁乙卯天中节书。袭具 单衫裤。(并以绵布。或麻布。)衣略著絮。裤亦著絮。 表衣内供䌷。(以上绵布。)单氅衣。(绵布。或麻布。)深衣(广麻布。缘用皂绢皂缯。)带。(麻布。或绢绅。缘用皂绢缯。)绦。(五色丝组成。无则青丝组。)袜。(绵布。)充耳。(雪绵为之。)幎目握手。(里并红帛。)幅巾。(以上黑绢。勿用毛缎。)方履。(白布为之。以缁或皂。为絇繶纯綦。)铭㫌。(中红絅。礼器尺七尺。)
敛具 绞。(麻布。)衾略施絮。(绵布。色则随宜。)道袍 倒衣。(以上麻布。或绵布。)补空。(绵布著絮。覆头面及补肩上者。用䌷制亦可。)
大敛具 绞。(麻布)衾。(绵布不著絮。或单衾。用单则麻布亦可。)道袍 倒衣。(以上绵布。或麻布。)
入棺具 棺。(松板厚薄。虽二寸五分。勿择山海所出。无白边无节轴则得矣。近世板贵。无此等病不易。削去边幅付板用之。凿去轴贯。填补用之。)涂棺。(废之可也。如难已。以洁白精纸涂之。又以古人之用。乃青红也而难之。用青红纸。勿用䌽帛。然青红之饰。终不若质素之好也。)地褥。(绵布表里。色随宜。)枕。(色䌷帛。)实棺。(随有不拘绵䌷布。但新制者。勿以䌷帛。)绛囊五。(绛䌷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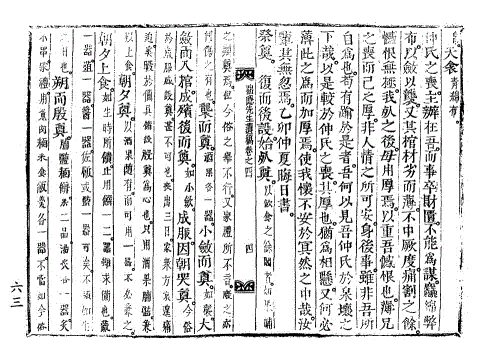 帛。)天衾(青绵布。)
帛。)天衾(青绵布。)仲氏之丧。主办在吾。而事卒财匮。不能为谋。粗绵弊布。以敛以袭。又其棺材劣而薄。不中厥度。痛割之馀。憾恨无极。我死之后。毋用厚焉。以重吾憾恨也。薄兄之丧而己之厚。非人情之所可安。身后事。虽非吾所自为也。苟有踰于是者。吾何以见吾仲氏于泉壤之下哉。以是较于仲氏之丧。其厚也。犹为相悬。又何必薄此之为而加厚焉。使我怀不安于冥然之中哉。汝辈其无忽焉。乙卯仲夏晦日书。
祭奠。 复而后设。始死奠。(以饮食之馀阁者。如果脯之类奠焉。但今俗之举不行。又家礼所不言。废之亦何伤之有也。)袭而奠。(酒果各一器。)小敛而奠。(如袭。)大敛而入棺。成殡后而奠。(如小敛。)成服。因朝哭奠。(今俗于成服盛设奠。甚不可也。丧出三日。家众方哀遑痛迫。奚暇于备具脩设殷奠为心也。只用酒果脯醢。兼以上食。)朝夕奠。(以酒果随有。而可用一器。不必兼之。)朝夕上食。(如生时所馈。止用馔一二。器虽求备也。蔬一器。菹一器。酱一器。佐饭或醢一器可矣。不须加生之日也。)朔而殷奠。(脯醢糆饼。果二品。汤炙各一器。炙不串。家礼。用鱼肉糆米食饭羹各一器。不当如今俗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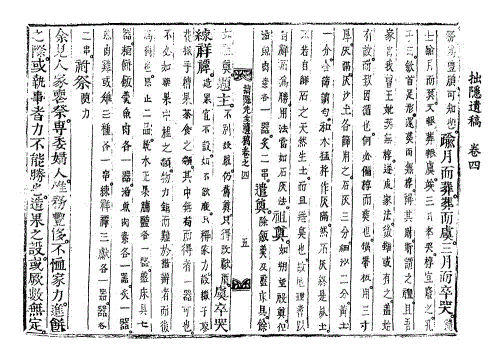 务为礼腆可知也。)踰月而葬。葬而虞。三月而卒哭。(礼士踰月而葬。又报葬报虞。俟三月卒哭。椁宜废之。孔子曰。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谓之礼。且吾家自我曾王妣葬无椁。遂成家法。后虽或有之。盖始有故。而致因循也。何必备椁而葬也。横带板。用三寸厚。灰隔。灰沙土各筛用之。石灰三分。细沙二分。黄土一分。合筛调匀。和水猛杵作灰隔。然石灰终是死土。不若自解石之天然生土。而且无臭也。故地理书以自解石为胜。用法当如石灰法。)祖奠。(如朔望殷奠。但汤鱼肉素各一器。炙二串。)遣奠。(除饭羹及盘床具。馀如祖奠。)题主。(不别设奠。仍旧奠。只得改献酒。)虞卒哭练祥禫。(造果宜不设。如不欲废。只称家力。设馓子蓼花撮手槽果茶食之类。其中无苟而得者一器可也。不必如药果中桂之类。物力钜而难于措办者而后为得也。果止二品。乾水正果脯醢各一器。盘床具七器。糆饼饭羹鱼肉各一器。汤鱼肉素各一器。炙一器。鱼肉鸡或雉三种各一串。练祥禫三献各一器。器各二串。)祔祭(随力)
务为礼腆可知也。)踰月而葬。葬而虞。三月而卒哭。(礼士踰月而葬。又报葬报虞。俟三月卒哭。椁宜废之。孔子曰。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谓之礼。且吾家自我曾王妣葬无椁。遂成家法。后虽或有之。盖始有故。而致因循也。何必备椁而葬也。横带板。用三寸厚。灰隔。灰沙土各筛用之。石灰三分。细沙二分。黄土一分。合筛调匀。和水猛杵作灰隔。然石灰终是死土。不若自解石之天然生土。而且无臭也。故地理书以自解石为胜。用法当如石灰法。)祖奠。(如朔望殷奠。但汤鱼肉素各一器。炙二串。)遣奠。(除饭羹及盘床具。馀如祖奠。)题主。(不别设奠。仍旧奠。只得改献酒。)虞卒哭练祥禫。(造果宜不设。如不欲废。只称家力。设馓子蓼花撮手槽果茶食之类。其中无苟而得者一器可也。不必如药果中桂之类。物力钜而难于措办者而后为得也。果止二品。乾水正果脯醢各一器。盘床具七器。糆饼饭羹鱼肉各一器。汤鱼肉素各一器。炙一器。鱼肉鸡或雉三种各一串。练祥禫三献各一器。器各二串。)祔祭(随力)余见人家丧祭。专委妇人。惟务丰侈。不恤家力。进饼之际。或执事者力不能胜也。造果之设。或厥数无定。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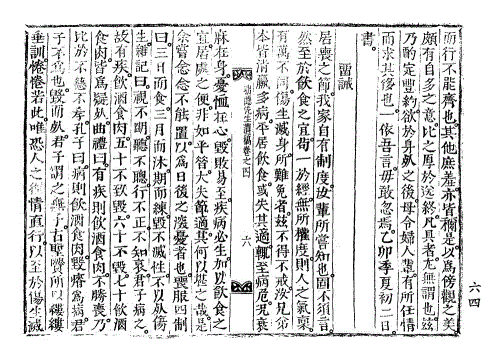 而行不能齐也。其他庶羞。亦皆称是。以为傍观之美。颇有自多之意。比之厚于送终。凡具者。尤无谓也。玆乃酌定丰约。欲于身死之后。毋令妇人辈。有所任情而求其侈也。一依吾言。毋敢忽焉。乙卯季夏初二日。书。
而行不能齐也。其他庶羞。亦皆称是。以为傍观之美。颇有自多之意。比之厚于送终。凡具者。尤无谓也。玆乃酌定丰约。欲于身死之后。毋令妇人辈。有所任情而求其侈也。一依吾言。毋敢忽焉。乙卯季夏初二日。书。留诫
居丧之节。我家自有制度。汝辈所尝知也。固不须言。然至于饮食之宜。苟一于经。无所权度。则人之气禀。有万不同。伤生灭身。所难免者。玆不得不戒。汝兄弟本皆清羸多病。平居饮食。或失其适。辄至病危。况衰麻在身。忧恤在心。毁败易至。疾病必生。加以饮食之宜。居处之便。非如平昔。大失节适。其何以堪之哉。是余尝念念不能置。以为日后之深忧者也。丧服四制曰。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杂记曰。视不明。听不聪。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饮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饮酒食肉。皆为疑死。曲礼曰。有疾则饮酒食肉。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孔子曰。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不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古圣贤所以缕缕垂训。惓惓若此。唯恐人之径情直行。以至于伤生灭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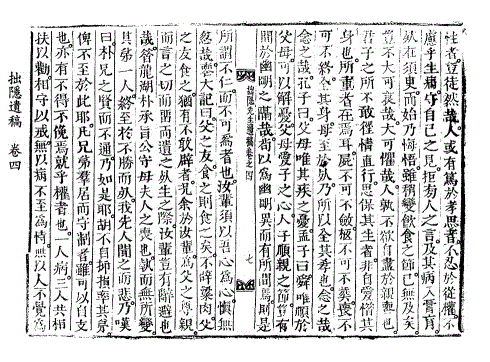 性者。岂徒然哉。人或有笃于孝思者。不忍于从权。不虑乎生病。守自己之见。拒旁人之言。及其病入膏肓。死在须臾。而始乃悔悟。虽稍变饮食之节。已无及矣。岂不大可哀哉。大可惧哉。人孰不欲自尽于亲丧也。君子之所不敢径情直行。思保其生者。非自爱惜其身也。所重者在焉耳。尸不可不敛。柩不可不葬。丧不可不终。全其身。毋至于死。乃所以全其孝也。念之哉念之哉。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子曰。舜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父母爱子之心。人子顺亲之节。岂有间于幽明之隔哉。苟以为幽明异而有所间焉。则是所谓不仁。而不可为者也。汝辈须以吾心为心。慎无忽哉。丧大记曰。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不辟粱肉。父之友食之。犹有不敢辟者。况余于汝辈。为父之尊亲。而言之切而留而遗之死生之际。汝辈岂有辞避也哉。昔龙湖朴承旨公守母夫人之丧也。执而无所变。其弟一人。终至于不胜而死。我先人闻之而悲。乃叹曰。朴兄之贤而不通。乃如是耶。胡不自抑损率其弟。俾不至于此耶。凡兄弟群居而守制者。虽可以自支也。亦有不得不俛焉就乎权者也。一人病。三人共相扶以劝。相守以戒。无以病不至为恃。无以人不觉为
性者。岂徒然哉。人或有笃于孝思者。不忍于从权。不虑乎生病。守自己之见。拒旁人之言。及其病入膏肓。死在须臾。而始乃悔悟。虽稍变饮食之节。已无及矣。岂不大可哀哉。大可惧哉。人孰不欲自尽于亲丧也。君子之所不敢径情直行。思保其生者。非自爱惜其身也。所重者在焉耳。尸不可不敛。柩不可不葬。丧不可不终。全其身。毋至于死。乃所以全其孝也。念之哉念之哉。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子曰。舜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父母爱子之心。人子顺亲之节。岂有间于幽明之隔哉。苟以为幽明异而有所间焉。则是所谓不仁。而不可为者也。汝辈须以吾心为心。慎无忽哉。丧大记曰。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不辟粱肉。父之友食之。犹有不敢辟者。况余于汝辈。为父之尊亲。而言之切而留而遗之死生之际。汝辈岂有辞避也哉。昔龙湖朴承旨公守母夫人之丧也。执而无所变。其弟一人。终至于不胜而死。我先人闻之而悲。乃叹曰。朴兄之贤而不通。乃如是耶。胡不自抑损率其弟。俾不至于此耶。凡兄弟群居而守制者。虽可以自支也。亦有不得不俛焉就乎权者也。一人病。三人共相扶以劝。相守以戒。无以病不至为恃。无以人不觉为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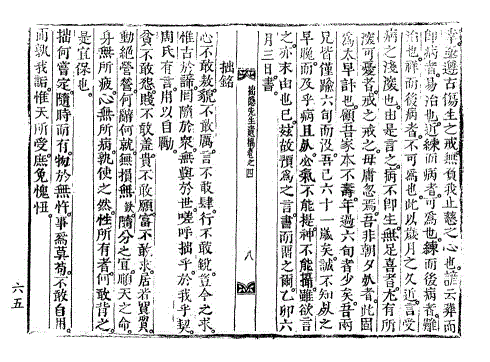 幸。亟遵古伤生之戒。无负我止慈之心也。谚云葬而即病者。易治也。近练而病者。可为也。练而后病者。难治也。祥而后病者。不可为也。此以岁月之久近。言受病之浅深也。由是言之。病不即生。无足喜者。尤有所深可忧者。戒之戒之。毋庸忽焉。吾非朝夕死者。此固为太早计也。顾吾家本不寿。年过六旬者少矣。吾两兄皆仅踰六旬而没。吾已六十一岁矣。诚不知死之早晚。而及乎病且死。必气不能提。神不能摄。虽欲言之。亦末由也已。玆故预为之言。书而留之尔。乙卯六月三日。书。
幸。亟遵古伤生之戒。无负我止慈之心也。谚云葬而即病者。易治也。近练而病者。可为也。练而后病者。难治也。祥而后病者。不可为也。此以岁月之久近。言受病之浅深也。由是言之。病不即生。无足喜者。尤有所深可忧者。戒之戒之。毋庸忽焉。吾非朝夕死者。此固为太早计也。顾吾家本不寿。年过六旬者少矣。吾两兄皆仅踰六旬而没。吾已六十一岁矣。诚不知死之早晚。而及乎病且死。必气不能提。神不能摄。虽欲言之。亦末由也已。玆故预为之言。书而留之尔。乙卯六月三日。书。拙铭
心不敢敖。貌不敢厉。言不敢肆。行不敢锐。岂今之求。惟古于谛。罔随于众。无与于世。嗟呼拙乎。于我乎契。周氏有言。用以自励。
贫不敢怨。贱不敢羞。贵不敢愿。富不敢求。居若贸贸。动绝营营。何辞何就。无损无(缺)。随分之宜。顺天之命。身无所疲。心无所病。孰使之然。性所有者。何敢背之。是宜保也。
拙何尝定。随时而有。物于无忤。事为莫苟。不敢自用。而孰我诟。惟天所受。庶免愧忸。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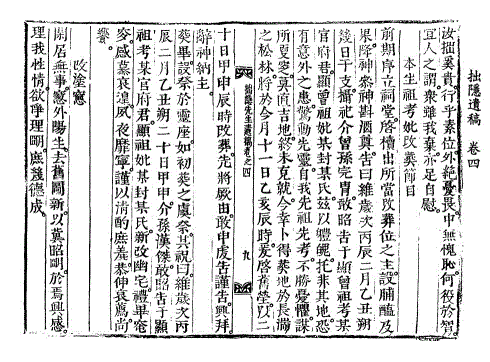 汝拙奚贵。行乎素位。外绝忧畏。中无愧耻。何役于智。宜人之谓。众虽我弃。亦足自慰。
汝拙奚贵。行乎素位。外绝忧畏。中无愧耻。何役于智。宜人之谓。众虽我弃。亦足自慰。本生祖考妣改葬节目
前期序立祠堂。启椟出所当改葬位之主。设脯醢及果。降神参神斟酒奠。告曰维岁次丙辰二月乙丑朔几日干支。摄祀介曾孙完胄。敢昭告于显曾祖考某官府君。显曾祖妣某封某氏。玆以体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患。惊动先灵。自我先祖先考。不胜忧惧。谋所更窆。莫直吉地。终未克就。今幸卜得葬地于长湍之松林。将于今月十一日乙亥辰时。爰启旧茔。以二十日甲申辰时改葬。先将厥由。敢申虔告谨告。兴拜。辞神纳主。
葬毕。设祭于灵座。如初葬之虞祭。其祝曰。维岁次丙辰二月乙丑朔二十日甲申。介孙汉杰。敢昭告于显祖考某官府君。显祖妣某封某氏。新改幽宅。礼毕窀穸。感慕哀遑。夙夜靡宁。谨以清酌庶羞。恭伸哀荐。尚飨。
改涂窗
闲居无事。窗外阳生。去旧图新。以冀昭明。于焉兴感。理我性情。欲净理明。庶几德成。
离奇枕铭
曰维楮公。赋形离奇。因其自然。作枕枕之。虽其嵬𡾋。曰安匪危。危之故安。孰为知斯。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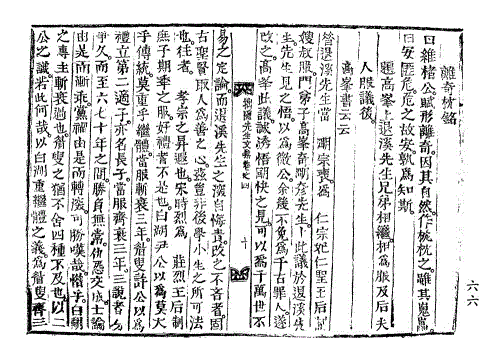 题高峰上退溪先生兄弟相继。相为服及后夫人服议后。
题高峰上退溪先生兄弟相继。相为服及后夫人服议后。高峰书云云
昔退溪先生当 明宗丧。为 仁宗妃仁圣王后制嫂叔服。门弟子高峰奇明彦先生。上此议于𨓆溪先生。先生见之悟。以为微公。余几不免为千古罪人。遂改之。高峰此议。诚透悟明快之见。可以为千万世不易之定论。而退溪先生之深自悔责。改之不吝者。固古圣贤取人为善之心。兹岂非后学小生之所可法也。往者。 孝宗之升遐也。宋时烈为 庄烈王后制庶子期䄵之服。好礼者不是也。白湖尹公以为莫大乎传统。莫重乎继体。当服斩衰三年。眉叟许公以为礼立第二适子。亦名长子。当服齐衰三年。三说者分争久。而至六七十年之间。胜负无常。仇怨交成。士论由是而渐乖。党祸由是而转深。可胜叹哉。惜乎。白湖之专主斩衰过也。眉叟之犹不舍四种不及也。以二公之识。若此何哉。以白湖重继体之义。为眉叟齐三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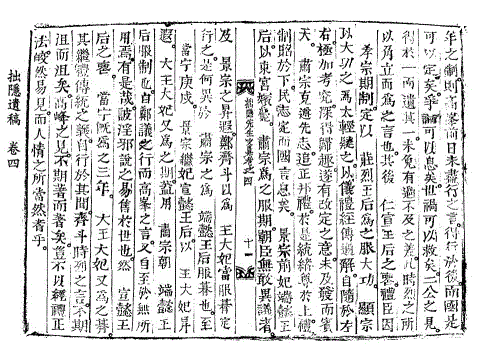 年之制。则高峰前日未尽行之言。得行于后。而国是可以定矣。争论可以息矣。世祸可以救矣。二公之见。得于一而遗其一。未免有过不及之差。此时烈之所以角立而为之言也。其后 仁宣王后之丧。礼臣因 孝宗期制。定以 庄烈王后为之服大功。 显宗以大功之为太轻疑之。以仪礼经传通解。自随于左右。极加考究。深得归趣。遂有改定之意。未及发而宾天。 肃宗克遵先志。追正邦礼。于是统绪尊于上。礼制昭于下。民志定而国言息矣。 景宗前妃端懿王后。以东宫嫔薨。 肃宗为之服期。朝臣无敢异议者。及 景宗之升遐。郑齐斗以为 王大妃当服期定行之。是何异于 肃宗之为 端懿王后服期也。至 当宁庚戌。 景宗继妃宣懿王后。以 王大妃升遐。 大王大妃又为之期。盖用 肃宗朝 端懿王后服制也。自郑议之行而高峰之言。又自至于无所用焉。有是哉。诐淫邪说之易售于世也。然 宣懿王后之丧。 当宁既为之三年。 大王大妃又为之期。其继体传统之义。自行于其间。齐斗时烈之言。不期沮而沮矣。高峰之见。不期著而著矣。岂不以经礼正法。皎然易见。而人情之所当然者乎。
年之制。则高峰前日未尽行之言。得行于后。而国是可以定矣。争论可以息矣。世祸可以救矣。二公之见。得于一而遗其一。未免有过不及之差。此时烈之所以角立而为之言也。其后 仁宣王后之丧。礼臣因 孝宗期制。定以 庄烈王后为之服大功。 显宗以大功之为太轻疑之。以仪礼经传通解。自随于左右。极加考究。深得归趣。遂有改定之意。未及发而宾天。 肃宗克遵先志。追正邦礼。于是统绪尊于上。礼制昭于下。民志定而国言息矣。 景宗前妃端懿王后。以东宫嫔薨。 肃宗为之服期。朝臣无敢异议者。及 景宗之升遐。郑齐斗以为 王大妃当服期定行之。是何异于 肃宗之为 端懿王后服期也。至 当宁庚戌。 景宗继妃宣懿王后。以 王大妃升遐。 大王大妃又为之期。盖用 肃宗朝 端懿王后服制也。自郑议之行而高峰之言。又自至于无所用焉。有是哉。诐淫邪说之易售于世也。然 宣懿王后之丧。 当宁既为之三年。 大王大妃又为之期。其继体传统之义。自行于其间。齐斗时烈之言。不期沮而沮矣。高峰之见。不期著而著矣。岂不以经礼正法。皎然易见。而人情之所当然者乎。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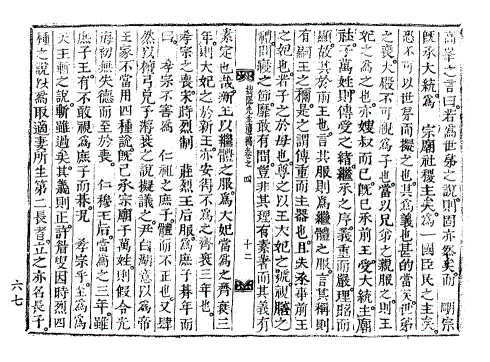 高峰之言曰。若为世弟之说。则固亦然矣。而 明宗既承大统。为 宗庙社稷主矣。为一国臣民之主矣。恐不可以世弟而拟之也。其为义也甚的当矣。世弟之丧。大殿不可视为子也。当以兄弟之亲服之。则王妃之为之也。亦嫂叔而已。既已承前王。受大统。主庙社。子万姓。则传受之绪。继承之序。义重而严。理昭而显。故其于前王也。言其服则为继体之服。言其称则有嗣王之称。是之谓传重而主器也。且夫承事前王之妃也。若子之于母也。尊之以王大妃之号。视膳之礼。问寝之节。靡敢有间。岂非其理有素著而其义有素定也哉。新王以继体之服。为大妃当为之齐衰三年。则大妃之于新王。亦安得不为之齐衰三年也。 孝宗之丧。宋时烈制 庄烈王后服。为庶子期年而曰。 孝宗不害为 仁祖之庶子。体而不正也。又肆然以檀弓兑(一作免)子游衰之说拟议之。尹白湖意以为帝王家不当用四种说。既已承宗庙子万姓。则假令光海初无失德而至于丧。 仁穆王后。当为之三年。虽庶子王。有不敢视为庶子而期。况 孝宗乎。至为为天王斩之说。斩虽过矣。其义则正。许眉叟因时烈四种之说以为取适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亦名长子。
高峰之言曰。若为世弟之说。则固亦然矣。而 明宗既承大统。为 宗庙社稷主矣。为一国臣民之主矣。恐不可以世弟而拟之也。其为义也甚的当矣。世弟之丧。大殿不可视为子也。当以兄弟之亲服之。则王妃之为之也。亦嫂叔而已。既已承前王。受大统。主庙社。子万姓。则传受之绪。继承之序。义重而严。理昭而显。故其于前王也。言其服则为继体之服。言其称则有嗣王之称。是之谓传重而主器也。且夫承事前王之妃也。若子之于母也。尊之以王大妃之号。视膳之礼。问寝之节。靡敢有间。岂非其理有素著而其义有素定也哉。新王以继体之服。为大妃当为之齐衰三年。则大妃之于新王。亦安得不为之齐衰三年也。 孝宗之丧。宋时烈制 庄烈王后服。为庶子期年而曰。 孝宗不害为 仁祖之庶子。体而不正也。又肆然以檀弓兑(一作免)子游衰之说拟议之。尹白湖意以为帝王家不当用四种说。既已承宗庙子万姓。则假令光海初无失德而至于丧。 仁穆王后。当为之三年。虽庶子王。有不敢视为庶子而期。况 孝宗乎。至为为天王斩之说。斩虽过矣。其义则正。许眉叟因时烈四种之说以为取适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亦名长子。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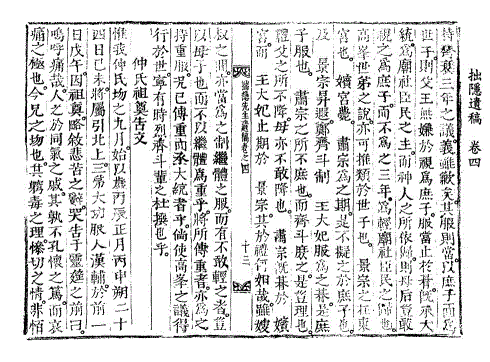 持齐衰三年之议。义虽歉矣。其服则当。以庶子而为世子。则父王无嫌于视为庶子。服当止于期。既承大统。为庙社臣民之主。而神人之所依归。则母后岂敢视之为庶子。而不为之三年。为轻庙社臣民之归也。高峰世弟之说。亦可推类于世子也。 景宗之在东宫也。 嫔宫薨。 肃宗为之期。是不拟之于庶子也。及 景宗升遐。郑齐斗制 王大妃服为之期。是庶子服也。 肃宗之所不庶也。而齐斗庶之。是岂理也。礼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肃宗既期于 嫔宫。而 王大妃止期于 景宗。其于礼何如哉。虽嫂叔之间。亦当为之制继体之服。而有不敢轻之者。岂以母子也而不以继体为重乎。将所传重者。亦为之持重服。况已传重而承大统者乎。倘使高峰之议得行于世。宁有时烈,齐斗辈之杜撰也乎。
持齐衰三年之议。义虽歉矣。其服则当。以庶子而为世子。则父王无嫌于视为庶子。服当止于期。既承大统。为庙社臣民之主。而神人之所依归。则母后岂敢视之为庶子。而不为之三年。为轻庙社臣民之归也。高峰世弟之说。亦可推类于世子也。 景宗之在东宫也。 嫔宫薨。 肃宗为之期。是不拟之于庶子也。及 景宗升遐。郑齐斗制 王大妃服为之期。是庶子服也。 肃宗之所不庶也。而齐斗庶之。是岂理也。礼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肃宗既期于 嫔宫。而 王大妃止期于 景宗。其于礼何如哉。虽嫂叔之间。亦当为之制继体之服。而有不敢轻之者。岂以母子也而不以继体为重乎。将所传重者。亦为之持重服。况已传重而承大统者乎。倘使高峰之议得行于世。宁有时烈,齐斗辈之杜撰也乎。仲氏祖奠告文
惟我仲氏殁之九月。始以岁丙辰正月丙申朔二十四日己未。将属引北上。三弟大功服人汉辅。于前一日戊午。因祖奠。略叙悲苦之辞。哭告于灵筵之前曰。呜呼痛哉。人之于同气之戚。其孰不孔怀之笃。而哀痛之极也。今兄之殁也。其䠻毒之理。惨切之情。非恒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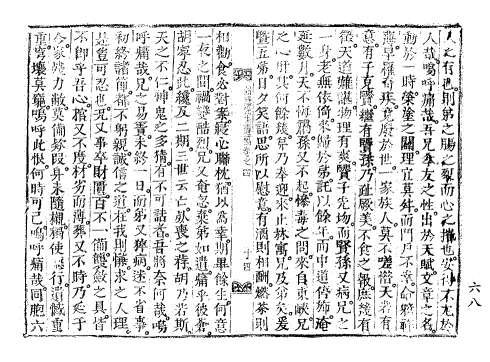 人之有也。则弟之肠之裂而心之摧也。安得不尤于人哉。呜呼痛哉。吾兄孝友之性。出于天赋。文章之名。动于一时。荣涂之辟。理宜莫舛。而门户不幸。命䠻祚薄。早罹奇疾。竟废于世。一家族人。莫不嗟惜。天若有意。有子克贤。继有贤孙。乃趾厥美。不食之报。庶几有徵。天道难谌。物理有爽。贤子先殁。而贤孙又病。兄之一身。老无依倚。来归于弟。托以馀年。而中道停旆。淹延数月。天不悔祸。孙又不起。惨毒之问。来自东峡。兄之心肝。其何馀几。弟乃奉迎。来止林寓。兄及弟矣。爰暨五弟。日夕笑语。思所以慰意。有酒则相酬。燃茶则相劝。食必对案。寝必联枕。犹以为幸。期毕馀生。何意一夜之间。祸变酷烈。兄又奄忽。弃弟如遗。痛乎彼苍。胡宁忍此。才及二期。三世云亡。死丧之荐。胡乃若斯。天之不仁。神鬼之多猜。有不可诘者。吾将奈何哉。呜呼痛哉。兄之易箦。未终一日。而弟又猝病。迷不省事。初终诸节。都不躬亲。诚信之道。在我则慊。求之人理。是岂可忍也。况又事卒财匮。百不一备。袭敛之具。皆不即乎吾心。棺又不度。材劣而薄。葬又不时。乃延于今。家残力敝。莫备款段。身未随榇。独使德行。遗憾重重。穹壤莫𥨪。呜呼此恨。何时可已。呜呼痛哉。同胞六
人之有也。则弟之肠之裂而心之摧也。安得不尤于人哉。呜呼痛哉。吾兄孝友之性。出于天赋。文章之名。动于一时。荣涂之辟。理宜莫舛。而门户不幸。命䠻祚薄。早罹奇疾。竟废于世。一家族人。莫不嗟惜。天若有意。有子克贤。继有贤孙。乃趾厥美。不食之报。庶几有徵。天道难谌。物理有爽。贤子先殁。而贤孙又病。兄之一身。老无依倚。来归于弟。托以馀年。而中道停旆。淹延数月。天不悔祸。孙又不起。惨毒之问。来自东峡。兄之心肝。其何馀几。弟乃奉迎。来止林寓。兄及弟矣。爰暨五弟。日夕笑语。思所以慰意。有酒则相酬。燃茶则相劝。食必对案。寝必联枕。犹以为幸。期毕馀生。何意一夜之间。祸变酷烈。兄又奄忽。弃弟如遗。痛乎彼苍。胡宁忍此。才及二期。三世云亡。死丧之荐。胡乃若斯。天之不仁。神鬼之多猜。有不可诘者。吾将奈何哉。呜呼痛哉。兄之易箦。未终一日。而弟又猝病。迷不省事。初终诸节。都不躬亲。诚信之道。在我则慊。求之人理。是岂可忍也。况又事卒财匮。百不一备。袭敛之具。皆不即乎吾心。棺又不度。材劣而薄。葬又不时。乃延于今。家残力敝。莫备款段。身未随榇。独使德行。遗憾重重。穹壤莫𥨪。呜呼此恨。何时可已。呜呼痛哉。同胞六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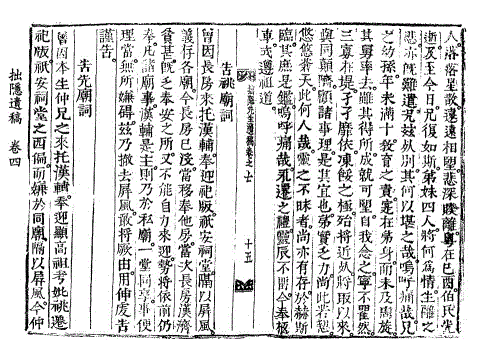 人。落落星散。远远相望。悲深睽离。粤在己酉。伯氏先逝。及至今日。兄复如斯。弟妹四人。将何为情。生离之悲。亦既难遣。况玆死别。其何以堪之哉。呜呼痛哉。兄之幼孙。年未满十。教育之责。寔在弟身。而未及周旋。其舅率去。虽其得所。成就可望。自我念之。宁不瞿然。三寡在堤。孑孑靡依。冻馁之极。殆将近死。将取以来。与同颠隮。顾诸事理。是其宜也。弟实乏力。尚此若恝。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灵之不昧者。尚亦有存。于赫斯临。其庶是鉴。呜呼痛哉。永迁之礼。灵辰不留。今奉柩车。式遵祖道。
人。落落星散。远远相望。悲深睽离。粤在己酉。伯氏先逝。及至今日。兄复如斯。弟妹四人。将何为情。生离之悲。亦既难遣。况玆死别。其何以堪之哉。呜呼痛哉。兄之幼孙。年未满十。教育之责。寔在弟身。而未及周旋。其舅率去。虽其得所。成就可望。自我念之。宁不瞿然。三寡在堤。孑孑靡依。冻馁之极。殆将近死。将取以来。与同颠隮。顾诸事理。是其宜也。弟实乏力。尚此若恝。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灵之不昧者。尚亦有存。于赫斯临。其庶是鉴。呜呼痛哉。永迁之礼。灵辰不留。今奉柩车。式遵祖道。告祧庙词
曾因长房来托汉辅。奉迎祀版。祇安祠堂。隔以屏风。义存各庙。今长房已没。当移奉他房。当次长房汉济贫甚。既乏奉安之所。又不能自力来迎。势将依前仍奉。凡诸庙事。汉辅是主。则乃于私庙。一堂同享。事便理当。无所嫌碍。玆乃撤去屏风。敢将厥由。用伸虔告谨告。
告先庙词
曾因本生仲兄之来托汉辅。奉迎显高祖考妣祧迁祀版。祇安祠堂之西偏。而嫌于同庙隔以屏风。今仲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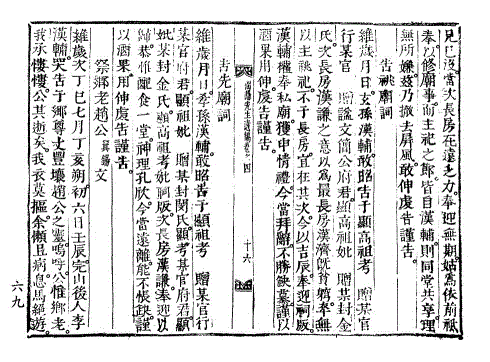 兄已没。当次长房在远乏力。奉迎无期。姑为依前祇奉。以修庙事。而主祀之节。皆自汉辅。则同堂共享。理无所嫌。玆乃撤去屏风。敢伸虔告谨告。
兄已没。当次长房在远乏力。奉迎无期。姑为依前祇奉。以修庙事。而主祀之节。皆自汉辅。则同堂共享。理无所嫌。玆乃撤去屏风。敢伸虔告谨告。告祧庙词
维岁月日。玄孙汉辅。敢昭告于显高祖考 赠某官行某官 赠谥文简公府君。显高祖妣 赠某封金氏。次长房汉谦之意以为最长房汉济既贫䠻。卒无以主祧祀。不于长房。宜在其次。今以吉辰。奉迎祠版。汉辅权奉私庙。获申情礼。今当拜辞。不胜缺慕。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
告先庙词
维岁月日。孝孙汉辅。敢昭告于显祖考 赠某官行某官府君。显祖妣 赠某封闵氏。显考某官府君。显妣某封金氏。显高祖考妣祠版。次长房汉谦。奉迎以归。恭惟配食一堂。神理孔欣。今当远离。能不怅缺。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
祭乡老赵公(箕锡)文
维岁次丁巳七月丁亥朔。初六日壬辰。完山后人李汉辅。哭告于乡尊丈丰壤赵公之灵。呜呼。公惟乡老。我承慺慺。公其逝矣。我衣莫抠。余懒且病。息马绝游。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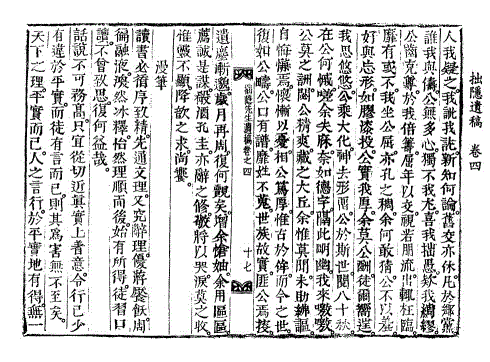 人我疑之。我訾我尤。新知何论。旧交亦休。凡于乡党。谁我与俦。公无多心。独不我尤。喜我拙愚。款我绸缪。公齿克尊。于我倍筹。屈年以交。视若朋流。出辄枉临。靡有或不。我坐公屈。亦孔之稠。余何敢猜。公不以羞。好与忘形。如胶漆投。公实我厚。余莫公酬。徒尔向𨓏。我思悠悠。公乘大化。神去形留。公于斯世。阅八十秋。有公何戚。嗟余失庥。奈如德宇。隔此明幽。我来噭噭。公莫之詶。閟公精爽。藏之大丘。余惟莫闻。未助绋讴。自悔慊焉。怀惭以忧。相公笃厚。惟古于侔。而今之世。复如公畴。公口有谱。靡姓不蒐。世族故实。匪公焉搜。遗尘渐邈。岁月再周。复何觌矣。增余怆妯。余用区区。荐诚是谋。殽酒孔圭。亦辞之修。敬将以哭。泪莫之收。惟灵不显。降歆之求。尚飨。
人我疑之。我訾我尤。新知何论。旧交亦休。凡于乡党。谁我与俦。公无多心。独不我尤。喜我拙愚。款我绸缪。公齿克尊。于我倍筹。屈年以交。视若朋流。出辄枉临。靡有或不。我坐公屈。亦孔之稠。余何敢猜。公不以羞。好与忘形。如胶漆投。公实我厚。余莫公酬。徒尔向𨓏。我思悠悠。公乘大化。神去形留。公于斯世。阅八十秋。有公何戚。嗟余失庥。奈如德宇。隔此明幽。我来噭噭。公莫之詶。閟公精爽。藏之大丘。余惟莫闻。未助绋讴。自悔慊焉。怀惭以忧。相公笃厚。惟古于侔。而今之世。复如公畴。公口有谱。靡姓不蒐。世族故实。匪公焉搜。遗尘渐邈。岁月再周。复何觌矣。增余怆妯。余用区区。荐诚是谋。殽酒孔圭。亦辞之修。敬将以哭。泪莫之收。惟灵不显。降歆之求。尚飨。漫笔
读书必循序致精。先通文理。又究辞理。优游餍饫。周遍融液。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后。始有所得。徒习口读。不曾致思。复何益哉。
话说不可务高。只宜从切近真实上着意。令行己少有违于平实。而徒有言而已。则其为害无不至矣。
天下之理。平实而已。人之言行。于平实地有得。无一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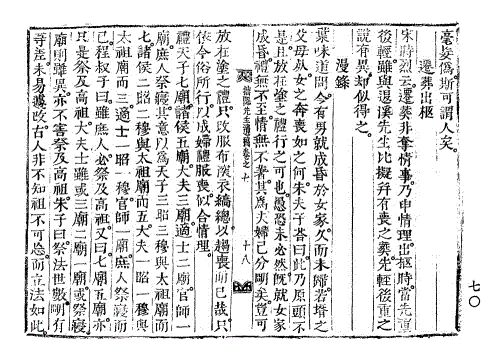 毫妄伪。斯可谓人矣。
毫妄伪。斯可谓人矣。迁葬出柩
宋时烈云。迁葬非夺情事。乃申情理。出柩时。当先重后轻。虽与𨓆溪先生比拟并有丧之葬。先轻后重之说有异。却似得之。
漫录
叶味道问。今有男就成昏于女家。久而未归。若婿之父母死。女之奔丧如之何。朱夫子答曰。此乃原头不是。且放在涂之礼行之可也。愚恐未必然。既就女家成昏。礼无不至。情无不著。其为夫妇已分明矣。岂可放在涂之礼。只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而已哉。只依今俗所行。以成妇礼服丧。似合情理。
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庶人祭寝。其意以为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庙而五。大夫一昭一穆与太祖庙而三。适士一昭一穆。官师一庙。庶人祭寝而已。程叔子曰。虽庶人。必祭及高祖。又曰。七庙五庙。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虽或三庙二庙一庙。或祭寝。庙则虽异。亦不害祭及高祖。朱子曰。祭法世数。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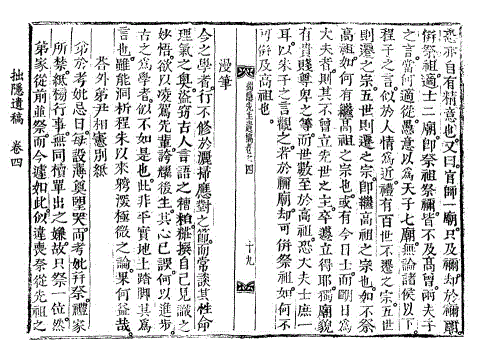 恐亦自有精意也。又曰。官师一庙。只及祢。却于祢庙。并祭祖。适士二庙。即祭祖祭祢。皆不及高曾。两夫子之言。当何适从。愚意以为天子七庙。无论诸侯以下。程子之言。似于人情为近。礼有百世不迁之宗。五世则迁之宗。五世则迁之宗。即继高祖之宗也。如不祭高祖。如何有继高祖之宗也。或有今日士。而明日为大夫者。则其不曾立先世之主。卒遽立得耶。独庙貌有贵贱尊卑之等。而世数至于高祖。恐大夫士庶一耳。以朱子之言观之。若于祢庙。却可并祭祖。如何不可并及高祖也。
恐亦自有精意也。又曰。官师一庙。只及祢。却于祢庙。并祭祖。适士二庙。即祭祖祭祢。皆不及高曾。两夫子之言。当何适从。愚意以为天子七庙。无论诸侯以下。程子之言。似于人情为近。礼有百世不迁之宗。五世则迁之宗。五世则迁之宗。即继高祖之宗也。如不祭高祖。如何有继高祖之宗也。或有今日士。而明日为大夫者。则其不曾立先世之主。卒遽立得耶。独庙貌有贵贱尊卑之等。而世数至于高祖。恐大夫士庶一耳。以朱子之言观之。若于祢庙。却可并祭祖。如何不可并及高祖也。漫笔
今之学者。行不修于洒扫应对之节。而常谈其性命理气之奥。盗窃古人言语之糟粕。妆撰自己见识之妙悟。欲以凌驾先辈。誇耀后生。其心已误。何以进步。古之为学者。似不如是也。此非平实地上踏脚其为言也。虽能洞析程朱以来䠻深极微之论。果何益哉。
答外弟尹相宪别纸
弟于考妣忌日。每设薄奠望哭。而考妣并祭。礼家所禁。纸榜行事。无同椟单出之嫌。故只祭一位。然弟家从前并祭。而今遽如此。似违丧祭从先祖之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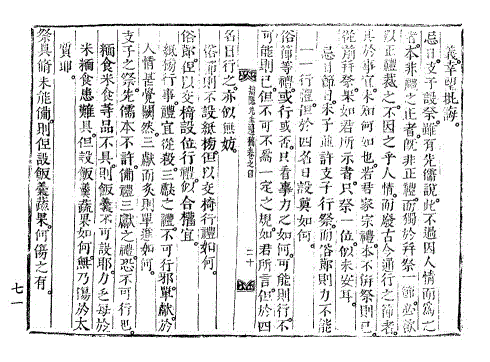 义。幸望批诲。
义。幸望批诲。忌日。支子设祭。虽有先儒说。此不过因人情而为之者。本非礼之正者。既非正礼。而独于并祭一节。必欲以正礼裁之。不因之乎人情。而废古今通行之节者。其于事宜。未知何如也。若君家宗礼。本不并祭则已。从前并祭。果如君所示者。只祭一位。似未安耳。
忌日节日。朱子并许支子行祭。而俗节则力不能一一行礼。但于四名日设奠如何。
俗节等礼。或行或否。只看事力之如何。可能则行。不可能则已。但不可不为一定之规。如君所言。但于四名日行之。亦似无妨。
俗节则不设纸榜。但以交椅行礼如何。
俗节。但以交椅设位行礼。似合权宜。
纸榜行事。礼宜从杀。三献之礼。不可行邪。单献。于人情甚觉阙然。三献而炙则单进如何。
支子之祭。先儒本不许。备礼三献之礼。恐不可行也。
糆食米食等品不具。则饭羹不可设耶。力乏每于米糆食患难具。但设饭羹蔬果如何。无乃伤于太质耶。
祭具脩未能备。则但设饭羹蔬果。何伤之有。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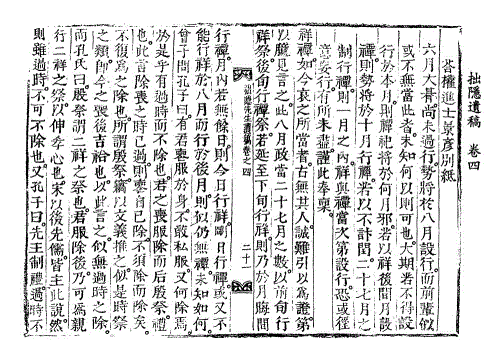 答权进士景彦别纸
答权进士景彦别纸六月大期。尚未过行。势将于八月设行。而前辈似或不无当此者。未知何以则可也。大期若不得设行于本月。则禫祀将于何月邪。若以祥后间月设禫。则势将于十月行禫。若以不计闰。二十七月之制行禫。则一月之内。祥与禫当次第设行。恐或径意妄行。有所未尽。谨此奉禀。
祥禫。如今哀之所当者。古无其人。诚难引以为證。第以臆见言之。此八月政当二十七月之数。以前旬行祥祭。后旬行禫祭。若延至下旬行祥。则乃于月晦间行禫。月内若无馀日。则今日行祥。明日行禫。或又不能行祥于八月而行于后月。则似仍无禫。未知如何。曾子问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过时而不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此言除丧之时已过。则丧自已除。不须除而除矣。不复为之除也。所谓殷祭。窃以文义推之。似是时祭之类。即今之丧后吉祫也。以此言之。似无过时之除。而孔氏曰。殷祭谓二祥之祭也。君服除后。乃可为亲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宋以后先儒。皆主此说。然则虽过时。不可不除也。又孔子曰。先王制礼。过时不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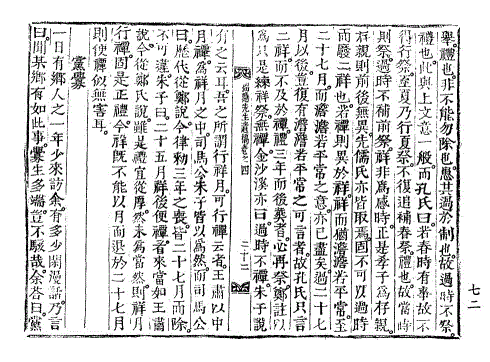 举。礼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过于制也。故过时不祭。礼也。此与上文意一般。而孔氏曰。若春时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复追补春祭。礼也。故当时则祭。过时不补前祭。祥非为感时。正是孝子为存亲。存亲则前后无异。先儒氏亦皆取焉。固不可以过时而废二祥也。若禫则异于祥。祥而犹澹澹若平常。至二十七月。而澹澹若平常之意。亦已尽矣。过二十七月以后。岂复有澹澹若平常之可言者。故孔氏只言二祥。而不及于禫。礼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郑注以为只是练祥祭。无禫。金沙溪亦曰。过时不禫。朱子说有之云耳。吾之所谓行祥月。可行禫云者。王肃以中月禫。为祥月之中。司马公,朱子皆以为然。而司马公曰。历代从郑说。今律敕三年之丧。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违。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后便禫。看来当如王肃说。今从郑氏说。虽是礼宜从厚。然未为当然。则祥月行禫。固是正礼。今祥既不能以月而退于二十七月则便禫似无害耳。
举。礼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过于制也。故过时不祭。礼也。此与上文意一般。而孔氏曰。若春时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复追补春祭。礼也。故当时则祭。过时不补前祭。祥非为感时。正是孝子为存亲。存亲则前后无异。先儒氏亦皆取焉。固不可以过时而废二祥也。若禫则异于祥。祥而犹澹澹若平常。至二十七月。而澹澹若平常之意。亦已尽矣。过二十七月以后。岂复有澹澹若平常之可言者。故孔氏只言二祥。而不及于禫。礼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郑注以为只是练祥祭。无禫。金沙溪亦曰。过时不禫。朱子说有之云耳。吾之所谓行祥月。可行禫云者。王肃以中月禫。为祥月之中。司马公,朱子皆以为然。而司马公曰。历代从郑说。今律敕三年之丧。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违。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后便禫。看来当如王肃说。今从郑氏说。虽是礼宜从厚。然未为当然。则祥月行禫。固是正礼。今祥既不能以月而退于二十七月则便禫似无害耳。党衅
一日有乡人之一年少来访余。有多少闲漫话。乃言曰。闻某乡有如此事。衅生多端。岂不骇哉。余答曰。党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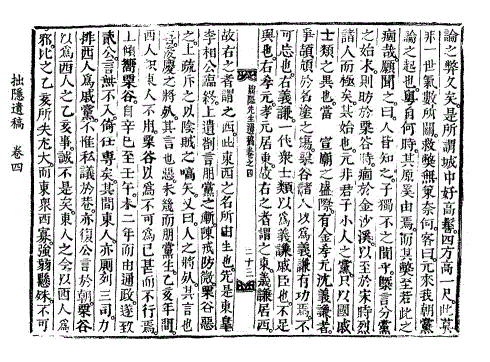 论之弊久矣。是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此莫非一世气数所关。救弊无策奈何。客曰。元来我朝党论之起也。粤自何时。其原奚由焉。而其弊至若此之痼哉。愿闻之。曰。人皆知之。子独不之闻乎。槩言分党之始末。则昉于栗谷时。痼于金沙溪。以至于宋时烈诸人而极矣。其始也。元非君子小人之党。只以国戚士类之异也。当 宣庙之盛际。有金孝元沈义谦者。争颉颃于名涂之场。栗谷诸人以为义谦有功焉。不可忘也。右义谦。一代众士类以为义谦戚臣也。不足与也。右孝元。孝元居东。故右之者谓之东。义谦居西。故右之者谓之西。此东西之名所由生也。先是东皋李相公临终。上遗劄言朋党之渐。陈戒防微。栗谷恶之。上疏斥之以阴贼之嗃矢。又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浚庆之将死。其言也恶。未几而朋党生。乙亥年间。西人只东人不用。栗谷以为不可为己甚而不行焉。上倾向栗谷。自辛巳至壬午。未二年而由通政。遂致贰公。言无不入。倚任专矣。其间东人。亦厕列三司。力排西人为戚党。不惟私议于巷。亦复公言于朝。栗谷以为西人之乙亥事。诚不是矣。东人之今以西人为邪。比之乙亥所失尤大。而东众西寡。强弱悬殊。不可
论之弊久矣。是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此莫非一世气数所关。救弊无策奈何。客曰。元来我朝党论之起也。粤自何时。其原奚由焉。而其弊至若此之痼哉。愿闻之。曰。人皆知之。子独不之闻乎。槩言分党之始末。则昉于栗谷时。痼于金沙溪。以至于宋时烈诸人而极矣。其始也。元非君子小人之党。只以国戚士类之异也。当 宣庙之盛际。有金孝元沈义谦者。争颉颃于名涂之场。栗谷诸人以为义谦有功焉。不可忘也。右义谦。一代众士类以为义谦戚臣也。不足与也。右孝元。孝元居东。故右之者谓之东。义谦居西。故右之者谓之西。此东西之名所由生也。先是东皋李相公临终。上遗劄言朋党之渐。陈戒防微。栗谷恶之。上疏斥之以阴贼之嗃矢。又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浚庆之将死。其言也恶。未几而朋党生。乙亥年间。西人只东人不用。栗谷以为不可为己甚而不行焉。上倾向栗谷。自辛巳至壬午。未二年而由通政。遂致贰公。言无不入。倚任专矣。其间东人。亦厕列三司。力排西人为戚党。不惟私议于巷。亦复公言于朝。栗谷以为西人之乙亥事。诚不是矣。东人之今以西人为邪。比之乙亥所失尤大。而东众西寡。强弱悬殊。不可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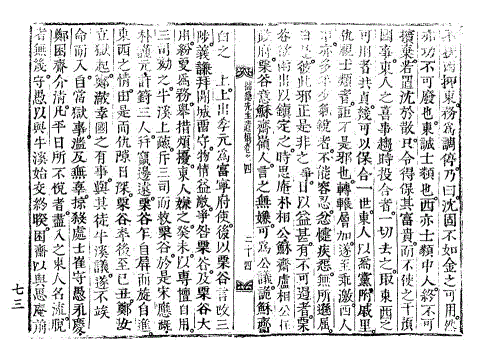 不扶西抑东。务为调停。乃曰。沈固不如金之可用。然亦功不可废也。东诚士类也。西亦士类中人。终不可摈弃。若置沈于散。只令得保其富贵。而不使之干预国事。东人之喜事趋时投合者。一切去之。取东西之可用者共贞。几可以保合一世。东人以为党附戚里。仇视士类者。讵不是邪也。转辗层加。遂至乖激。西人中。亦多年少气锐者。不能容忍。忿懥疾怨。无所逊屈。由是。彼此邪正是非之争。日以益甚。有不可遏者。栗谷欲两出以镇定之。时思庵朴相公,稣斋卢相公在政府。栗谷意稣斋岭人。言之无嫌。可为公议。诡稣斋白之 上。上出孝元为富宁府使。后以栗谷言改三陟。义谦拜开城留守。物情益激。争咎栗谷。及栗谷大用。纷更为务。举措烦扰。东人嫌之。癸未。以专擅自用。三司劾之。牛溪上疏。斥三司而救栗谷。于是宋应溉,朴谨元,许篈三人。并窜边远。栗谷乍自屏而旋自进。东西之情。由是而仇隙日深。栗谷卒后至己丑。郑汝立狱起。郑澈幸国之有事。与其徒牛溪议。遂不俟 命而入。自当狱事。滥及无辜。掠杀处士崔守愚永庆,郑困斋介清。凡平日所不悦者。尽入之东人名流。脱者无几。守愚以与牛溪始交终睽。困斋以与思庵前
不扶西抑东。务为调停。乃曰。沈固不如金之可用。然亦功不可废也。东诚士类也。西亦士类中人。终不可摈弃。若置沈于散。只令得保其富贵。而不使之干预国事。东人之喜事趋时投合者。一切去之。取东西之可用者共贞。几可以保合一世。东人以为党附戚里。仇视士类者。讵不是邪也。转辗层加。遂至乖激。西人中。亦多年少气锐者。不能容忍。忿懥疾怨。无所逊屈。由是。彼此邪正是非之争。日以益甚。有不可遏者。栗谷欲两出以镇定之。时思庵朴相公,稣斋卢相公在政府。栗谷意稣斋岭人。言之无嫌。可为公议。诡稣斋白之 上。上出孝元为富宁府使。后以栗谷言改三陟。义谦拜开城留守。物情益激。争咎栗谷。及栗谷大用。纷更为务。举措烦扰。东人嫌之。癸未。以专擅自用。三司劾之。牛溪上疏。斥三司而救栗谷。于是宋应溉,朴谨元,许篈三人。并窜边远。栗谷乍自屏而旋自进。东西之情。由是而仇隙日深。栗谷卒后至己丑。郑汝立狱起。郑澈幸国之有事。与其徒牛溪议。遂不俟 命而入。自当狱事。滥及无辜。掠杀处士崔守愚永庆,郑困斋介清。凡平日所不悦者。尽入之东人名流。脱者无几。守愚以与牛溪始交终睽。困斋以与思庵前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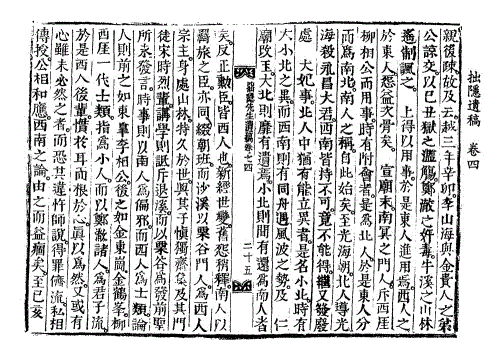 亲后疏。故及云。越三年辛卯。李山海与金贵人之弟公谅交。以己丑狱之滥觞。郑澈之奸毒。牛溪之山林遥制讽之。 上得以用事。于是东人进用焉。西人之于东人。怨益次骨矣。 宣庙末。南冥之门人。斥西厓柳相公而用事。时有附会者。是为北人。于是东人分而为南北。南人之称。自此始矣。至光海朝。北人导光海杀永昌大君。西南皆持不可。竟不能得。继又发废处 大妃事。北人中犹有能立异者。是名小北。时有大小北之异。而西南则有同舟遇风波之势。及 仁庙改玉。大北则靡有遗焉。小北则间有还为南人者矣。反正勋臣。皆西人也。新经世变。旧怨稍释。南人以羁旅之臣。亦同缀朝班。而沙溪以栗谷门人。为西人宗主。身处山林。特久于世。与其子慎独斋集及其门徒宋时烈辈。讲学则诋斥退溪。而以栗谷为发前圣所未发言。时事则以南人为偏邪。而西人为士类。论人则前之如东皋李相公。后之如金东岗,金鹤峰。柳西厓一代士类。指为小人。而以郑澈诸人。为君子流。于是西人后辈。惯于耳而根于心。真以为然。又或有心虽未必然之者。而恐其违忤师说。得罪侪流。私相传授。公相和应。西南之论。由之而益痼矣。至己亥
亲后疏。故及云。越三年辛卯。李山海与金贵人之弟公谅交。以己丑狱之滥觞。郑澈之奸毒。牛溪之山林遥制讽之。 上得以用事。于是东人进用焉。西人之于东人。怨益次骨矣。 宣庙末。南冥之门人。斥西厓柳相公而用事。时有附会者。是为北人。于是东人分而为南北。南人之称。自此始矣。至光海朝。北人导光海杀永昌大君。西南皆持不可。竟不能得。继又发废处 大妃事。北人中犹有能立异者。是名小北。时有大小北之异。而西南则有同舟遇风波之势。及 仁庙改玉。大北则靡有遗焉。小北则间有还为南人者矣。反正勋臣。皆西人也。新经世变。旧怨稍释。南人以羁旅之臣。亦同缀朝班。而沙溪以栗谷门人。为西人宗主。身处山林。特久于世。与其子慎独斋集及其门徒宋时烈辈。讲学则诋斥退溪。而以栗谷为发前圣所未发言。时事则以南人为偏邪。而西人为士类。论人则前之如东皋李相公。后之如金东岗,金鹤峰。柳西厓一代士类。指为小人。而以郑澈诸人。为君子流。于是西人后辈。惯于耳而根于心。真以为然。又或有心虽未必然之者。而恐其违忤师说。得罪侪流。私相传授。公相和应。西南之论。由之而益痼矣。至己亥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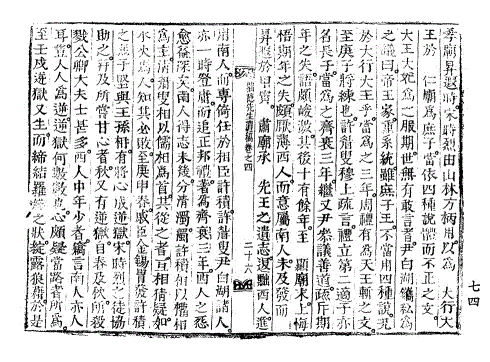 孝庙升遐时。宋时烈由山林方柄用。以为 大行大王于 仁庙为庶子。当依四种说体而不正之文。 大王大妃为之服期。世无有敢言者。尹白湖鑴私为之议曰。帝王家。重系统。虽庶子王。不当用四种说。况于大行大王乎。当为之三年。周礼有为天王斩之文。至庚子将练也。许眉叟穆上疏言。礼立第二适子亦名长子。当为之齐衰三年。继又尹参议善道。疏斥期年之失。语颇峻激。其后十有馀年。至 显庙末。上悔悟期年之失。颇厌薄西人。而意属南人。未及发而 升遐于甲寅。 肃庙承 先王之遗志。𨓆黜西人。进用南人。而专倚任于相臣许积。许眉叟尹白湖诸人。亦一时登庸。而追正邦礼。著为齐衰三年。西人之怨。愈益深矣。南人得志未几。分清浊。浊许积相以权相为主。清眉叟相以儒相为首。其从之者。互相猜疑。如水火焉。人知其必败。至庚申春。戚臣金锡胄发许积之庶子坚与王孙楠。有将心成逆狱。宋时烈之徒协助之。并及所尝甘心者。秋又有逆狱。自春及秋。所杀戮公卿大夫士甚多。西人中年少者。窃言南人亦人耳。岂人人为逆。逆狱何数数也。心颇疑当路者所为。至壬戌逆狱又生。而缔结罗织之状。绽露狼藉。于是
孝庙升遐时。宋时烈由山林方柄用。以为 大行大王于 仁庙为庶子。当依四种说体而不正之文。 大王大妃为之服期。世无有敢言者。尹白湖鑴私为之议曰。帝王家。重系统。虽庶子王。不当用四种说。况于大行大王乎。当为之三年。周礼有为天王斩之文。至庚子将练也。许眉叟穆上疏言。礼立第二适子亦名长子。当为之齐衰三年。继又尹参议善道。疏斥期年之失。语颇峻激。其后十有馀年。至 显庙末。上悔悟期年之失。颇厌薄西人。而意属南人。未及发而 升遐于甲寅。 肃庙承 先王之遗志。𨓆黜西人。进用南人。而专倚任于相臣许积。许眉叟尹白湖诸人。亦一时登庸。而追正邦礼。著为齐衰三年。西人之怨。愈益深矣。南人得志未几。分清浊。浊许积相以权相为主。清眉叟相以儒相为首。其从之者。互相猜疑。如水火焉。人知其必败。至庚申春。戚臣金锡胄发许积之庶子坚与王孙楠。有将心成逆狱。宋时烈之徒协助之。并及所尝甘心者。秋又有逆狱。自春及秋。所杀戮公卿大夫士甚多。西人中年少者。窃言南人亦人耳。岂人人为逆。逆狱何数数也。心颇疑当路者所为。至壬戌逆狱又生。而缔结罗织之状。绽露狼藉。于是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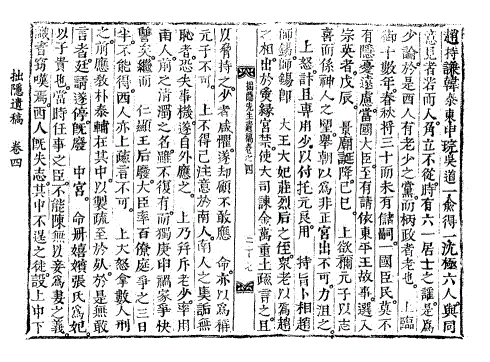 赵持谦,韩泰东,申琓,吴道一,俞得一,沈极六人。与同意见者若而人。角立不从。时有六一居士之谣。是为少论。于是西人有老少之党。而柄政者老也。 上临御十数年。春秋将三十而未有储嗣。一国臣民。莫不有隐忧远虑。当国大臣。至有请依东平王故事。选入宗英者。戊辰。 景庙诞降。己巳。 上欲称元子以志喜而系神人之望。举朝以为非正宫出不可。力沮之。 上怒。计且专用少。以付托元良。用 特旨卜相赵师锡。师锡即 大王大妃庄烈后之侄。众老以为赵之相。出于夤缘宫禁。使大司谏金万重上疏言之。且以胁持之。少者咸惧。遂却顾不敢应 命。亦以为称元子不可。 上不得已注意于南人。南人之奊诟无耻者。恐失事机。遂自外应之。 上乃并斥老少。率用南人。前之清浊之名。虽不复有。而独庚申祸家争快雠矣。继而 仁显王后废。大臣率百僚庭争之三日半。不能得。西人亦上疏言不可。 上大怒拿数人刑之。前应教朴泰辅在其中。以制疏至于死。于是无敢言者。廷请遂停。既废 中宫。 命册嬉嫔张氏为妃。以子贵也。当时任事之臣。不能陈无以妾为妻之义。识者窃叹焉。西人既失志。其中不逞之徒。设上中下
赵持谦,韩泰东,申琓,吴道一,俞得一,沈极六人。与同意见者若而人。角立不从。时有六一居士之谣。是为少论。于是西人有老少之党。而柄政者老也。 上临御十数年。春秋将三十而未有储嗣。一国臣民。莫不有隐忧远虑。当国大臣。至有请依东平王故事。选入宗英者。戊辰。 景庙诞降。己巳。 上欲称元子以志喜而系神人之望。举朝以为非正宫出不可。力沮之。 上怒。计且专用少。以付托元良。用 特旨卜相赵师锡。师锡即 大王大妃庄烈后之侄。众老以为赵之相。出于夤缘宫禁。使大司谏金万重上疏言之。且以胁持之。少者咸惧。遂却顾不敢应 命。亦以为称元子不可。 上不得已注意于南人。南人之奊诟无耻者。恐失事机。遂自外应之。 上乃并斥老少。率用南人。前之清浊之名。虽不复有。而独庚申祸家争快雠矣。继而 仁显王后废。大臣率百僚庭争之三日半。不能得。西人亦上疏言不可。 上大怒拿数人刑之。前应教朴泰辅在其中。以制疏至于死。于是无敢言者。廷请遂停。既废 中宫。 命册嬉嫔张氏为妃。以子贵也。当时任事之臣。不能陈无以妾为妻之义。识者窃叹焉。西人既失志。其中不逞之徒。设上中下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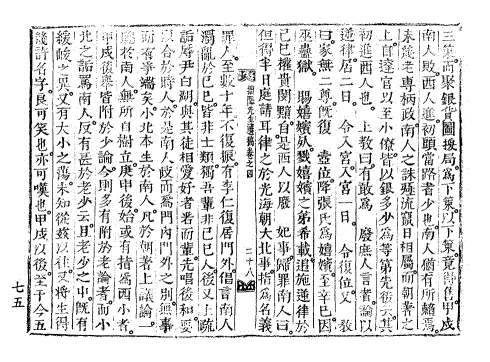 三策。而聚银货图换局。为下策。以下策。竟得售。甲戌南人败。西人进。初头当路者少也。南人犹有所赖焉。未几老专柄政。南人之诛殛流窜日相属。而朝著之上。自达官以至小僚。皆以银多少为等第先后云。其初进西人也。 上教曰。有敢为 废庶人言者。论以逆律。居二日。 令入宫。入宫一日。 令复位。又 教曰。家无二尊。既复 壸位。降张氏为嬉嫔。至辛巳。因巫蛊狱。 赐嬉嫔死。戮嬉嫔之弟希载。追施逆律于己巳权贵闵黯。自是西人以废 妃事。归罪南人曰。但得半日庭请耳。律之于光海朝大北事。指为名义罪人。至数十年。不复振。有李仁复居门外。倡言南人浊乱于己巳。皆非士类。独吾辈非己巳人。后又上疏诟辱尹白湖。与其徒相爱好若者而辈。先唱后和。要以合于时人。于是南人歧而为门内门外之别。无事而有争端矣。小北本生于南人。凡于朝著上议论。一听于南人。无所自树立。庚申后。始或有指为西小者。甲戌后举皆附于少论。今则多有附于老论者。而小北之诟骂南人。反有甚于老少云。且老少之中。既有缓峻之异。又有大小之荡。未知从玆以往。又将生得几许名字。良可笑也。亦可叹也。甲戌以后。至于今五
三策。而聚银货图换局。为下策。以下策。竟得售。甲戌南人败。西人进。初头当路者少也。南人犹有所赖焉。未几老专柄政。南人之诛殛流窜日相属。而朝著之上。自达官以至小僚。皆以银多少为等第先后云。其初进西人也。 上教曰。有敢为 废庶人言者。论以逆律。居二日。 令入宫。入宫一日。 令复位。又 教曰。家无二尊。既复 壸位。降张氏为嬉嫔。至辛巳。因巫蛊狱。 赐嬉嫔死。戮嬉嫔之弟希载。追施逆律于己巳权贵闵黯。自是西人以废 妃事。归罪南人曰。但得半日庭请耳。律之于光海朝大北事。指为名义罪人。至数十年。不复振。有李仁复居门外。倡言南人浊乱于己巳。皆非士类。独吾辈非己巳人。后又上疏诟辱尹白湖。与其徒相爱好若者而辈。先唱后和。要以合于时人。于是南人歧而为门内门外之别。无事而有争端矣。小北本生于南人。凡于朝著上议论。一听于南人。无所自树立。庚申后。始或有指为西小者。甲戌后举皆附于少论。今则多有附于老论者。而小北之诟骂南人。反有甚于老少云。且老少之中。既有缓峻之异。又有大小之荡。未知从玆以往。又将生得几许名字。良可笑也。亦可叹也。甲戌以后。至于今五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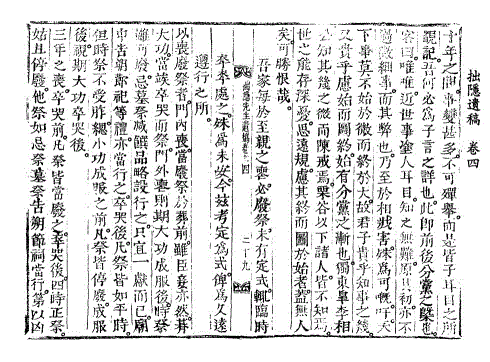 十年之间。事变甚多。不可殚举。而是皆子耳目之所睹记。吾何必为子言之详也。此即前后分党之槩也。客曰。唯唯。近世事涂人耳目。知之无难。原其初。亦不过微细事。而其弊也。乃至于相戕害。殊为可嘅。吁。天下事莫不始于微而终于大。故君子贵乎知事之几。又贵乎虑始而图终。始有分党之渐也。独东皋李相公知其几之微而陈戒焉。栗谷以下诸人。皆不知焉。世之能存深忧。思远规。虑其终而图于始者。盖无人矣。可胜恨哉。
十年之间。事变甚多。不可殚举。而是皆子耳目之所睹记。吾何必为子言之详也。此即前后分党之槩也。客曰。唯唯。近世事涂人耳目。知之无难。原其初。亦不过微细事。而其弊也。乃至于相戕害。殊为可嘅。吁。天下事莫不始于微而终于大。故君子贵乎知事之几。又贵乎虑始而图终。始有分党之渐也。独东皋李相公知其几之微而陈戒焉。栗谷以下诸人。皆不知焉。世之能存深忧。思远规。虑其终而图于始者。盖无人矣。可胜恨哉。吾家每于至亲之丧。必废祭。未有定式。辄临时卒卒处之。殊为未安。今玆考定为式。俾为久远遵行之所。
以丧废祭者。门内丧。当废祭于葬前。虽臣妾亦然。期大功。当俟卒哭而祭。门外丧则期大功成服后。时祭虽可废。忌墓祭减馔品略设行之。只宜一献而已。庙中告朔节祀等礼。亦当行之。卒哭后。凡祭皆如平时。但时祭不受胙。缌小功成服之前。凡祭皆停废。成服后。视期大功卒哭后。
三年之丧。卒哭前。凡祭皆当废之。卒哭后。四时正祭。姑且停废。他祭如忌祭,墓祭告朔节祠当行。第以凶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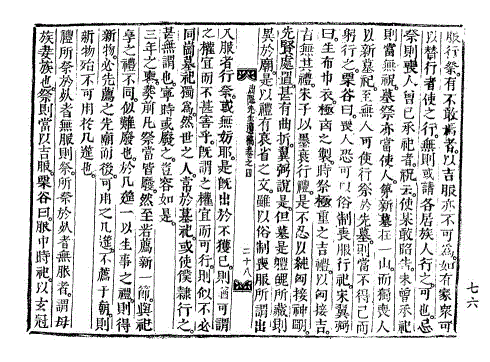 服行祭。有不敢焉者。以吉服亦不可为。如有家众可以替行者使之行。无则或请各居族人行之。可也。忌祭则丧人曾已承祀者。祝云。使某敢昭告。未曾承祀则当无祝。墓祭亦当使人。第新墓在一山。而独丧人以新墓祀。至无人可使行祭于先墓。则当不得已而躬行之。栗谷曰。丧人恐可以俗制丧服行祀。宋翼弼曰。生布巾衣。极凶之制。时祭极重之吉礼。以匈接吉。古无其礼。朱子以墨衰行礼。是不忍以纯匈接神明。先贤处置。甚有曲折。翼弼说是。但墓是体魄所藏则异于庙。是以礼有哀省之文。虽以俗制丧服所谓出入服者行祭。或无妨耶。是既出于不获已。则犹可谓之权宜而不甚害乎。既谓之权宜而可行。则似不必同岗墓祀独为。然世之人。常于墓祀。或使仆隶行之。甚无谓也。宁时或废之。岂容如是。
服行祭。有不敢焉者。以吉服亦不可为。如有家众可以替行者使之行。无则或请各居族人行之。可也。忌祭则丧人曾已承祀者。祝云。使某敢昭告。未曾承祀则当无祝。墓祭亦当使人。第新墓在一山。而独丧人以新墓祀。至无人可使行祭于先墓。则当不得已而躬行之。栗谷曰。丧人恐可以俗制丧服行祀。宋翼弼曰。生布巾衣。极凶之制。时祭极重之吉礼。以匈接吉。古无其礼。朱子以墨衰行礼。是不忍以纯匈接神明。先贤处置。甚有曲折。翼弼说是。但墓是体魄所藏则异于庙。是以礼有哀省之文。虽以俗制丧服所谓出入服者行祭。或无妨耶。是既出于不获已。则犹可谓之权宜而不甚害乎。既谓之权宜而可行。则似不必同岗墓祀独为。然世之人。常于墓祀。或使仆隶行之。甚无谓也。宁时或废之。岂容如是。三年之丧。葬前凡祭当皆废。然至若荐新一节。与祀享之礼不同。似难废也。于几筵一以生事之礼。则得新物。必先荐之先庙而后。可用之几筵。不荐于庙。则新物殆不可用于几筵也。
礼所祭于死者无服则祭。所祭于死者无服者。谓母族妻族也。祭则当以吉服。栗谷曰。服巾(一作中)时祀。以玄冠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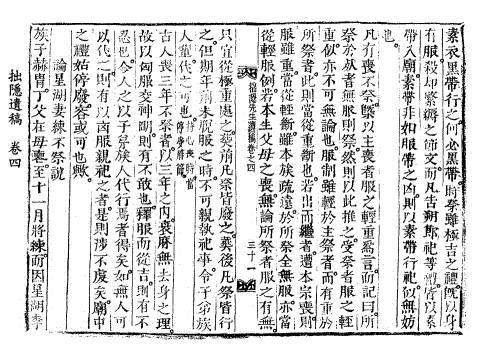 素衣黑带行之。何必黑带。时祭虽极吉之礼。既以身有服。杀却繁缛之节文。而凡告朔节祀等礼。皆以素带入庙。素带非如服带之凶。则以素带行祀。似无妨也。
素衣黑带行之。何必黑带。时祭虽极吉之礼。既以身有服。杀却繁缛之节文。而凡告朔节祀等礼。皆以素带入庙。素带非如服带之凶。则以素带行祀。似无妨也。凡有丧不祭。槩以主丧者服之轻重为言。而记曰。所祭于死者无服则祭。然则以此推之。受祭者服之轻重。似亦不可无论也。服制虽轻于主祭者。而有重于所祭者。此则当从重断也。若出而继者。遭本宗丧。则服虽重。当从轻断。虽本族疏远。于所祭全无服。亦当从轻服例。若本生父母之丧。无论所祭者服之有无。只宜从极重处之。葬前凡祭皆废之。葬后凡祭皆行之。但期年前未脱服之时。不可亲执祀事。令子弟族人辈。代之可也。(持心丧时。当停受胙节。)
古人丧三年不祭者。以三年之内。衰麻无去身之理。故以匈服交神明。则有不敢也。释服而从吉。则有不忍也。今人之以子弟族人代行焉者得矣。如无人可以代之。则有以凶服亲祀之者。是则涉不虔矣。庙中之礼姑停废。容或可也欤。
论星湖妻练不祭说
族子赫胄。丁父在母丧。至十一月将练。而因星湖李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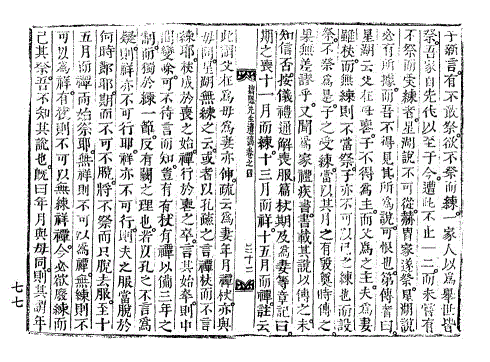 子新言。有不敢祭。欲不祭而练。一家人以为举世皆祭。吾家自先代以至于今。遭此不止一二。而未尝有不祭而受练者。星湖说不可从。赫胄家遂祭。星湖说必有所据。而吾不得见其所为说。可恨也。第传者曰。星湖云父在母丧。子不得为主。而父为之主。夫为妻虽杖。而无练则不当祭。子亦不可以己之练也而设祭。不祭为是。子之受练。当以其月之有殷奠时传之。果无差谬乎。又闻为家礼疾书。书载其说以传之。未知信否。按仪礼通解丧服篇杖期及为妻等章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谓父在为母为妻亦伸。疏云为妻年月禫杖。亦与母同。星湖无练之云。或者以孔疏之言禫杖而不言练耶。杖成于丧之始。禫行于丧之卒。言其始卒。则中间变除。可不待言而知。岂有有杖有禫以备三年之制。而独于练一节。反有阙之理也。若以孔之不言为疑。则祥亦不可行耶。祥亦不可行。则夫之服当脱于何时节耶。期而不可不脱。将不祭而只脱去服。至十五月而禫而始祭耶。无祥则不可以为禫。无练则不可以为祥。有杖则不可以无练祥禫。今必欲废练而已其祭。吾不知其说也。既曰年月与母同。则其谓年
子新言。有不敢祭。欲不祭而练。一家人以为举世皆祭。吾家自先代以至于今。遭此不止一二。而未尝有不祭而受练者。星湖说不可从。赫胄家遂祭。星湖说必有所据。而吾不得见其所为说。可恨也。第传者曰。星湖云父在母丧。子不得为主。而父为之主。夫为妻虽杖。而无练则不当祭。子亦不可以己之练也而设祭。不祭为是。子之受练。当以其月之有殷奠时传之。果无差谬乎。又闻为家礼疾书。书载其说以传之。未知信否。按仪礼通解丧服篇杖期及为妻等章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谓父在为母为妻亦伸。疏云为妻年月禫杖。亦与母同。星湖无练之云。或者以孔疏之言禫杖而不言练耶。杖成于丧之始。禫行于丧之卒。言其始卒。则中间变除。可不待言而知。岂有有杖有禫以备三年之制。而独于练一节。反有阙之理也。若以孔之不言为疑。则祥亦不可行耶。祥亦不可行。则夫之服当脱于何时节耶。期而不可不脱。将不祭而只脱去服。至十五月而禫而始祭耶。无祥则不可以为禫。无练则不可以为祥。有杖则不可以无练祥禫。今必欲废练而已其祭。吾不知其说也。既曰年月与母同。则其谓年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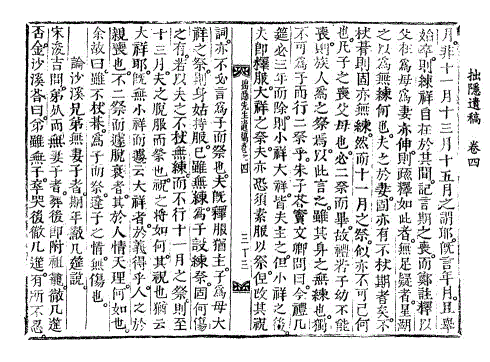 月。非十一月十三月十五月之谓耶。既言年月。且举始卒。则练祥自在于其间。记言期之丧。而郑注释以父在为母为妻亦伸。则疏释如此者。无足疑者。星湖之以为无练何也。夫之于妻。固亦有不杖期者矣。不杖期则固亦无练。然而十一月之祭。似亦不可已何也。凡子之丧父母也。必二祭而毕。故礼若子幼不能丧。则族人为之祭焉。以此言之。虽其身之无练也。独不可为子而行二祭乎。朱子答窦文卿问曰。今礼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小祥大祥。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后。夫即释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须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词。亦不必言为子而祭也。夫既释服犹主。子为母大祥之祭。则身姑持服。己虽无练。为子设练祭。固何伤之有。若以夫之不杖无练。而不行十一月之祭。则至十三月。夫之脱服而祭也。祝之将如何。其祝也犹云大祥耶。既无小祥而遽云大祥者。于义得乎。人之于亲丧也。不二祭而遽脱衰者。其于人情天理。何如也。余故曰。虽不杖期。为子而祭。达子之情。无伤也。
月。非十一月十三月十五月之谓耶。既言年月。且举始卒。则练祥自在于其间。记言期之丧。而郑注释以父在为母为妻亦伸。则疏释如此者。无足疑者。星湖之以为无练何也。夫之于妻。固亦有不杖期者矣。不杖期则固亦无练。然而十一月之祭。似亦不可已何也。凡子之丧父母也。必二祭而毕。故礼若子幼不能丧。则族人为之祭焉。以此言之。虽其身之无练也。独不可为子而行二祭乎。朱子答窦文卿问曰。今礼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小祥大祥。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后。夫即释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须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词。亦不必言为子而祭也。夫既释服犹主。子为母大祥之祭。则身姑持服。己虽无练。为子设练祭。固何伤之有。若以夫之不杖无练。而不行十一月之祭。则至十三月。夫之脱服而祭也。祝之将如何。其祝也犹云大祥耶。既无小祥而遽云大祥者。于义得乎。人之于亲丧也。不二祭而遽脱衰者。其于人情天理。何如也。余故曰。虽不杖期。为子而祭。达子之情。无伤也。论沙溪兄弟无妻子者。期年撤几筵说。
宋浚吉问。弟死而无妻子者。葬后即附祖龛。彻几筵否。金沙溪答曰。弟虽无子。卒哭后彻几筵。有所不忍。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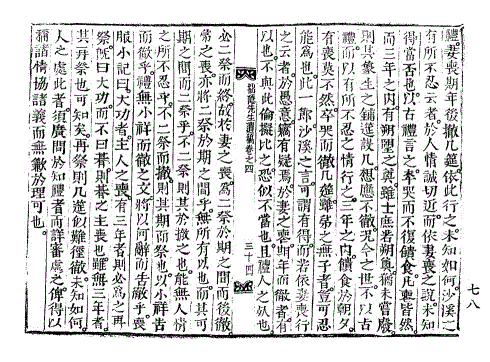 礼。妻丧期年后撤几筵。依此行之。未知如何。沙溪之有所不忍云者。于人情诚切近。而依妻丧之说。未知得当否也。以古礼言之。卒哭而不复馈食。凡丧皆然。而三年之内。有朔望之奠。虽士庶若朔奠。犹未尝废。则其象生之铺筵设几。想应不彻。况今之世。不以古礼。而以有所不忍之情行之。三年之内。馈食于朝夕。有丧莫不然。卒哭而彻几筵。虽弟之无子者。岂可忍能为也。此一节。沙溪之言。可谓有得。而若依妻丧行之云者。于愚意。窃有疑焉。于妻之丧。期年而彻者。有以也。不与此伦拟比之。恐似不当也。且礼人之死也。必二祭而终。故于妻之丧。为二祭于期之间而后彻。弟之丧。亦将二祭于期之间乎。无所有以也。而其可期之间而二祭乎。不二祭则其于撤之也。能无人情之所不忍乎。不二祭而撤。则其期而祭也。以小祥告而彻乎。礼无小祥而彻之文。将以何辞而告彻乎。丧服小记曰。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既曰大功。而不曰期。则期之主丧也。虽无三年者。其再祭也可知矣。再祭则几筵似难径彻。未知如何。人之处此者。须广问于知礼者而详审处之。俾得以称诸情协诸义而无歉于理可也。
礼。妻丧期年后撤几筵。依此行之。未知如何。沙溪之有所不忍云者。于人情诚切近。而依妻丧之说。未知得当否也。以古礼言之。卒哭而不复馈食。凡丧皆然。而三年之内。有朔望之奠。虽士庶若朔奠。犹未尝废。则其象生之铺筵设几。想应不彻。况今之世。不以古礼。而以有所不忍之情行之。三年之内。馈食于朝夕。有丧莫不然。卒哭而彻几筵。虽弟之无子者。岂可忍能为也。此一节。沙溪之言。可谓有得。而若依妻丧行之云者。于愚意。窃有疑焉。于妻之丧。期年而彻者。有以也。不与此伦拟比之。恐似不当也。且礼人之死也。必二祭而终。故于妻之丧。为二祭于期之间而后彻。弟之丧。亦将二祭于期之间乎。无所有以也。而其可期之间而二祭乎。不二祭则其于撤之也。能无人情之所不忍乎。不二祭而撤。则其期而祭也。以小祥告而彻乎。礼无小祥而彻之文。将以何辞而告彻乎。丧服小记曰。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既曰大功。而不曰期。则期之主丧也。虽无三年者。其再祭也可知矣。再祭则几筵似难径彻。未知如何。人之处此者。须广问于知礼者而详审处之。俾得以称诸情协诸义而无歉于理可也。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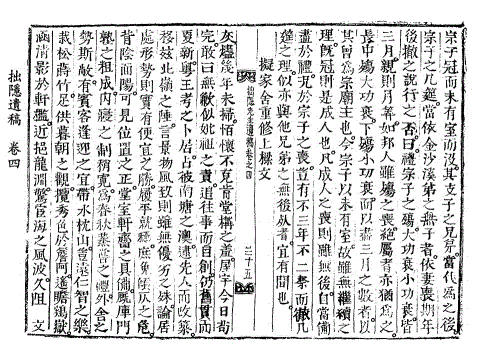 宗子冠而未有室而没。其支子之兄弟。当代为之后。宗子之几筵。当依金沙溪弟之无子者。依妻丧期年后撤之说行之否。曰。礼宗子之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虽殇之丧。绝属者亦犹为之。长,中殇大功衰。下殇小功衰。而以尽三月之数者。以其曾为宗庙主也。今宗子以未有室。故虽无继续之理。既冠则是成人也。凡成人之丧则虽无后。自当备尽于礼。况于宗子之丧。岂有不三年不二祭而彻几筵之理。似亦与他兄弟之无后死者。宜有间也。
宗子冠而未有室而没。其支子之兄弟。当代为之后。宗子之几筵。当依金沙溪弟之无子者。依妻丧期年后撤之说行之否。曰。礼宗子之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虽殇之丧。绝属者亦犹为之。长,中殇大功衰。下殇小功衰。而以尽三月之数者。以其曾为宗庙主也。今宗子以未有室。故虽无继续之理。既冠则是成人也。凡成人之丧则虽无后。自当备尽于礼。况于宗子之丧。岂有不三年不二祭而彻几筵之理。似亦与他兄弟之无后死者。宜有间也。拟家舍重修上梁文
灰烬几年未扫。恒怀不克肯堂构之羞。屋宇今日苟完。敢曰无歉似妣祖之责。追往事而自创。仍旧贯而更新。粤王考之卜居。占彼南塘之澳。逮先人而改筑。移玆北岭之陲。言景物风致则虽无优劣之殊。论居处形势则实有便宜之胜。履平就稳。庶免倾仄之危。背阴面阳。可见位置之正。堂室轩斋之具备。厩库门塾之粗成。内寝之制稍宽。为春秋蒸尝之礼。外舍之势斯敞。有宾客逢迎之宜。带水枕山。岂远仁智之乐。栽松莳竹。足供暮朝之观。揽秀色于檐阿。遥瞻鸡岳。涵清影于轩槛。近挹龙渊。惊宦海之风波。久阻 文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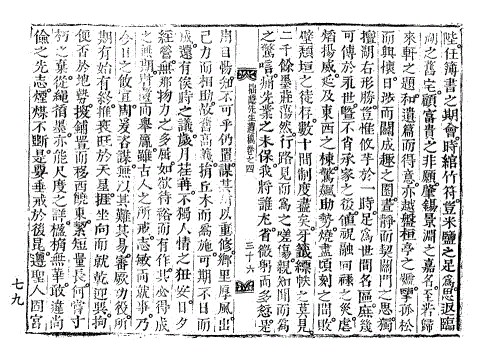 陛。任簿书之期会。时绾竹符。岂米盐之足为。思返临湖之旧宅。顾富贵之非愿。肇锡景渊之嘉名。至若归来轩之题。和遗篇而得意。亦越盘桓亭之号。揽孤松而兴怀。日涉而辟成趣之园。昼静而契关门之思。独擅湖右形胜。岂惟攸芋于一时。足为世间名区。庶几可传于永世。暨不肖承家之后。值祝融回禄之灾。虐焰扬威。延及东西之栋。惊飙助势。烧尽顷刻之间。败壁颓垣之徒存。数十间制度尽矣。牙签缥帙之莫见。二千馀墨庄荡然。行路见而为之嗟伤。亲知闻而为之惊唁。痛先业之未保。我将谁尤。省微躬而多愆。是用自惕。知不可乎仍置。谋其所以重修。乡里厚风。出己力而相助。故旧高义。捐丘木而为施。可期不日而成。还有俟时之议。岁月荏苒。不独人情之狃安。日夕经营。无那物力之多屈。如欲待裕而有作。其必得成之无期。财匮而举赢。虽古人之所戒。志敏而就事。乃今日之攸宜。周爰咨谋。无以其难其易。审厥功役。所期有始有终。推衰旺于天星。挨坐向而就乾迎巽。拘便否于地势。换铺置而移西饶东。絜短量长。何尝寸朽之弃。从绳循墨。亦能尺度之详。楹桷无华。敢违尚俭之先志。烟煤不斲。是要垂戒于后昆。遵圣人固宫
陛。任簿书之期会。时绾竹符。岂米盐之足为。思返临湖之旧宅。顾富贵之非愿。肇锡景渊之嘉名。至若归来轩之题。和遗篇而得意。亦越盘桓亭之号。揽孤松而兴怀。日涉而辟成趣之园。昼静而契关门之思。独擅湖右形胜。岂惟攸芋于一时。足为世间名区。庶几可传于永世。暨不肖承家之后。值祝融回禄之灾。虐焰扬威。延及东西之栋。惊飙助势。烧尽顷刻之间。败壁颓垣之徒存。数十间制度尽矣。牙签缥帙之莫见。二千馀墨庄荡然。行路见而为之嗟伤。亲知闻而为之惊唁。痛先业之未保。我将谁尤。省微躬而多愆。是用自惕。知不可乎仍置。谋其所以重修。乡里厚风。出己力而相助。故旧高义。捐丘木而为施。可期不日而成。还有俟时之议。岁月荏苒。不独人情之狃安。日夕经营。无那物力之多屈。如欲待裕而有作。其必得成之无期。财匮而举赢。虽古人之所戒。志敏而就事。乃今日之攸宜。周爰咨谋。无以其难其易。审厥功役。所期有始有终。推衰旺于天星。挨坐向而就乾迎巽。拘便否于地势。换铺置而移西饶东。絜短量长。何尝寸朽之弃。从绳循墨。亦能尺度之详。楹桷无华。敢违尚俭之先志。烟煤不斲。是要垂戒于后昆。遵圣人固宫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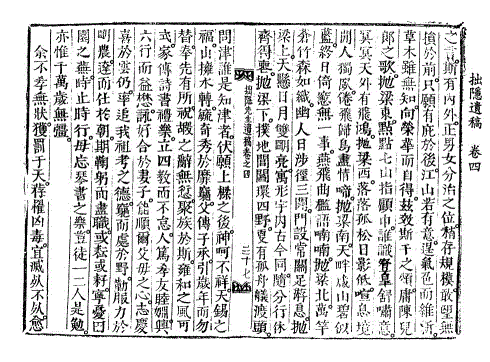 之言。斯有内外。正男女分治之位。稍存规模。敢望无损于前。只愿有庇于后。江山若有意。逞气色而维新。草木虽无知。向荣华而自得。玆效斯干之颂。庸陈儿郎之歌。抛梁东。点点七山指顾中。谁识登皋舒啸意。冥冥天外有飞鸿。抛梁西。落落孤松日影低。喧息境閒人独卧。倦飞归鸟尽情啼。抛梁南。天畔咸山碧似蓝。终日倚窗无一事。燕飞曲槛语喃喃。抛梁北。万竿苍竹森如织。幽人日涉径三开。门设常关足游息。抛梁上。天悬日月双明亮。寓形宇内古今同。随分行休齐得丧。抛梁下。扑地闾阎环四野。更有孤舟舣渡头。问津谁是知津者。伏愿上梁之后。神呵不祥。天锡之福。山拥水转。毓奇秀于靡𥨪。父传子承。引岁年而勿替。奉先有所。祝嘏之辞无愆。聚族于斯。雍和之风可式。家传诗书礼乐。立四教而不怠。人笃孝友睦姻。兴六行而益懋。咏好合于妻子。能顺尔父母之心。志庆喜于云仍。率追我祖考之德。𥨪而处于野。勤服力于明农。达而仕于朝。期鞠躬而尽职。或耘或耔。宁忧田园之芜。时止时行。毋忘琴书之乐。岂徒一二人是勉。亦惟千万岁无彊。
之言。斯有内外。正男女分治之位。稍存规模。敢望无损于前。只愿有庇于后。江山若有意。逞气色而维新。草木虽无知。向荣华而自得。玆效斯干之颂。庸陈儿郎之歌。抛梁东。点点七山指顾中。谁识登皋舒啸意。冥冥天外有飞鸿。抛梁西。落落孤松日影低。喧息境閒人独卧。倦飞归鸟尽情啼。抛梁南。天畔咸山碧似蓝。终日倚窗无一事。燕飞曲槛语喃喃。抛梁北。万竿苍竹森如织。幽人日涉径三开。门设常关足游息。抛梁上。天悬日月双明亮。寓形宇内古今同。随分行休齐得丧。抛梁下。扑地闾阎环四野。更有孤舟舣渡头。问津谁是知津者。伏愿上梁之后。神呵不祥。天锡之福。山拥水转。毓奇秀于靡𥨪。父传子承。引岁年而勿替。奉先有所。祝嘏之辞无愆。聚族于斯。雍和之风可式。家传诗书礼乐。立四教而不怠。人笃孝友睦姻。兴六行而益懋。咏好合于妻子。能顺尔父母之心。志庆喜于云仍。率追我祖考之德。𥨪而处于野。勤服力于明农。达而仕于朝。期鞠躬而尽职。或耘或耔。宁忧田园之芜。时止时行。毋忘琴书之乐。岂徒一二人是勉。亦惟千万岁无彊。余不孝无状。获罚于天。荐罹凶毒。宜灭死不死。愈
拙隐先生遗稿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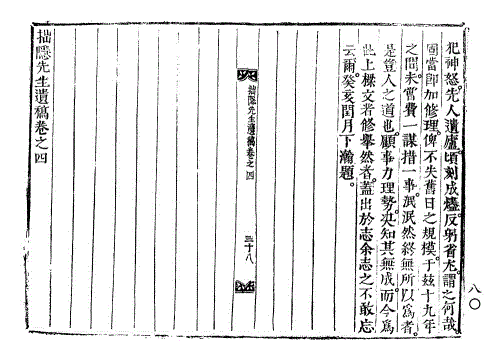 犯神怒。先人遗庐。顷刻成烬。反躬省尤。谓之何哉。固当即加修理。俾不失旧日之规模。于玆十九年之间。未尝费一谋措一事。泯泯然终无所以为者。是岂人之道也。顾事力理势。决知其无成。而今为此上梁文若修举然者。盖出于志余志之不敢忘云尔。癸亥闰月下瀚题。
犯神怒。先人遗庐。顷刻成烬。反躬省尤。谓之何哉。固当即加修理。俾不失旧日之规模。于玆十九年之间。未尝费一谋措一事。泯泯然终无所以为者。是岂人之道也。顾事力理势。决知其无成。而今为此上梁文若修举然者。盖出于志余志之不敢忘云尔。癸亥闰月下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