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x 页
栎翁遗稿卷之五
讲义
讲义
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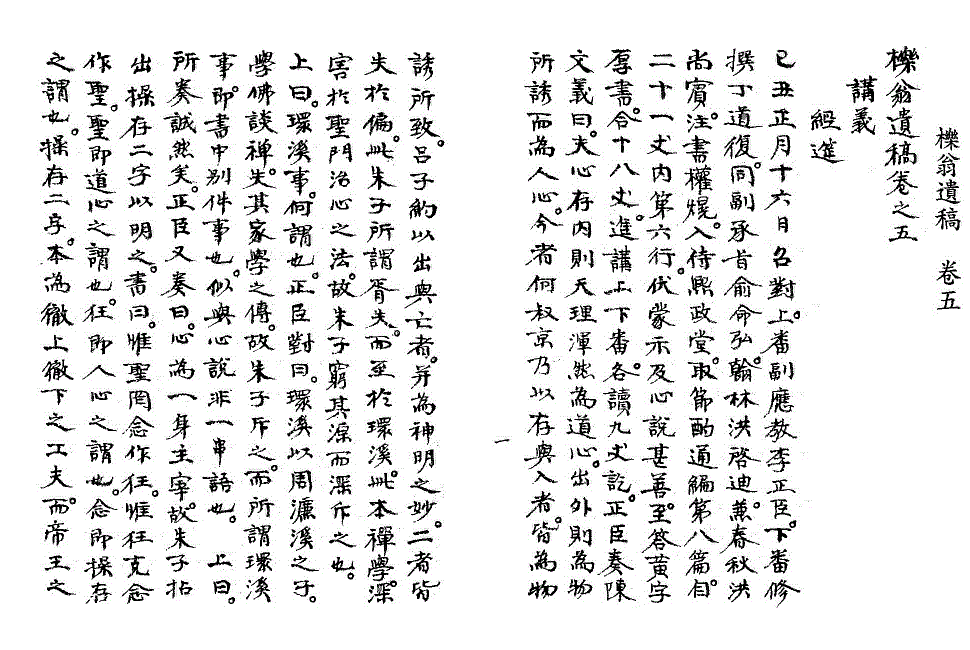 经筵
经筵己丑正月十六日召对。上番副应教李正臣。下番修撰丁道复。同副承旨俞命弘。翰林洪启迪。兼春秋洪尚宾。注书权熀。入侍熙政堂。取节酌通编第八篇。自二十一丈内第六行。伏蒙示及心说甚善。至答黄字厚书。合十八丈。进讲上下番。各读九丈讫。正臣奏陈文义曰。夫心存内则天理浑然为道心。出外则为物所诱而为人心。今者何叔京乃以存与入者。皆为物诱所致。吕子约以出与亡者。并为神明之妙。二者皆失于偏。此朱子所谓胥失。而至于环溪。此本禅学。深害于圣门治心之法。故朱子穷其源而深斥之也。 上曰。环溪事。何谓也。正臣对曰。环溪以周濂溪之子。学佛谈禅。失其家学之传。故朱子斥之。而所谓环溪事。即书中别件事也。似与心说非一串语也。 上曰。所奏诚然矣。正臣又奏曰。心为一身主宰。故朱子拈出操存二字以明之。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即道心之谓也。狂即人心之谓也。念即操存之谓也。操存二字。本为彻上彻下之工夫。而帝王之
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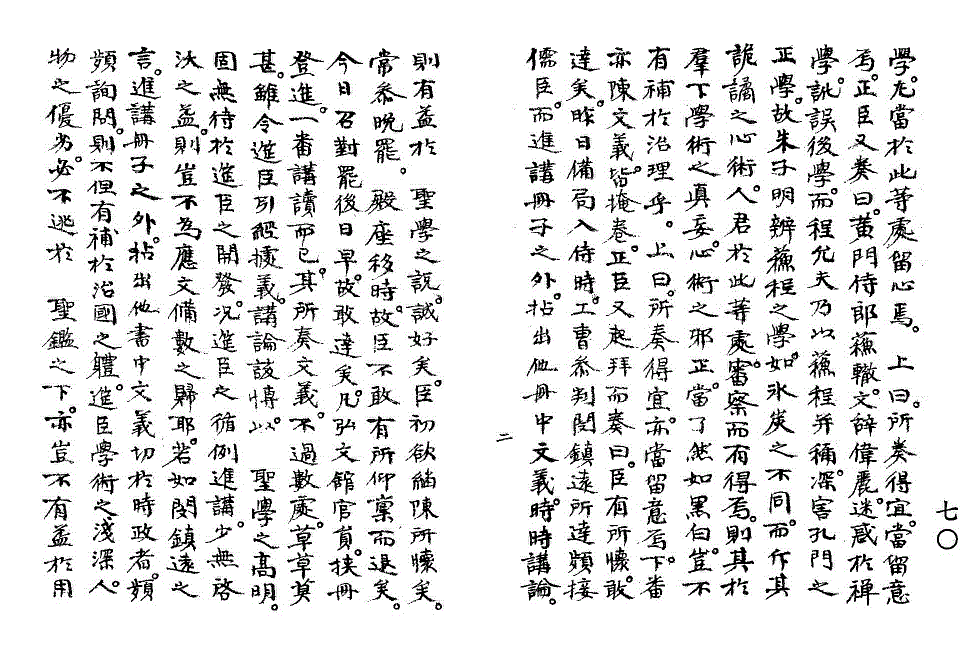 学。尤当于此等处留心焉。 上曰。所奏得宜。当留意焉。正臣又奏曰。黄门侍郎苏辙。文辞伟丽。迷惑于禅学。讹误后学。而程允夫乃以苏程并称。深害孔门之正学。故朱子明辨苏程之学。如冰炭之不同。而斥其诡谲之心术。人君于此等处。审察而有得焉。则其于群下学术之真妄。心术之邪正。当了然如黑白。岂不有补于治理乎。 上曰。所奏得宜。亦当留意焉。下番亦陈文义。皆掩卷。正臣又起拜而奏曰。臣有所怀。敢达矣。昨日备局入侍时。工曹参判闵镇远所达频接儒臣。而进讲册子之外。拈出他册中文义。时时讲论。则有益于 圣学之说。诚好矣。臣初欲继陈所怀矣。常参晚罢。 殿座移时。故臣不敢有所仰禀而退矣。今日召对罢后日早。故敢达矣。凡弘文馆官员。挟册登进。一番讲读而已。其所奏文义。不过数处。草草莫甚。虽令筵臣引经据义。讲论该博。以 圣学之高明。固无待于筵臣之开发。况筵臣之循例进讲。少无启沃之益。则岂不为应文备数之归耶。若如闵镇远之言。进讲册子之外。拈出他书中文义切于时政者。频频询问。则不但有补于治国之体。筵臣学术之浅深。人物之优劣。必不逃于 圣鉴之下。亦岂不有益于用
学。尤当于此等处留心焉。 上曰。所奏得宜。当留意焉。正臣又奏曰。黄门侍郎苏辙。文辞伟丽。迷惑于禅学。讹误后学。而程允夫乃以苏程并称。深害孔门之正学。故朱子明辨苏程之学。如冰炭之不同。而斥其诡谲之心术。人君于此等处。审察而有得焉。则其于群下学术之真妄。心术之邪正。当了然如黑白。岂不有补于治理乎。 上曰。所奏得宜。亦当留意焉。下番亦陈文义。皆掩卷。正臣又起拜而奏曰。臣有所怀。敢达矣。昨日备局入侍时。工曹参判闵镇远所达频接儒臣。而进讲册子之外。拈出他册中文义。时时讲论。则有益于 圣学之说。诚好矣。臣初欲继陈所怀矣。常参晚罢。 殿座移时。故臣不敢有所仰禀而退矣。今日召对罢后日早。故敢达矣。凡弘文馆官员。挟册登进。一番讲读而已。其所奏文义。不过数处。草草莫甚。虽令筵臣引经据义。讲论该博。以 圣学之高明。固无待于筵臣之开发。况筵臣之循例进讲。少无启沃之益。则岂不为应文备数之归耶。若如闵镇远之言。进讲册子之外。拈出他书中文义切于时政者。频频询问。则不但有补于治国之体。筵臣学术之浅深。人物之优劣。必不逃于 圣鉴之下。亦岂不有益于用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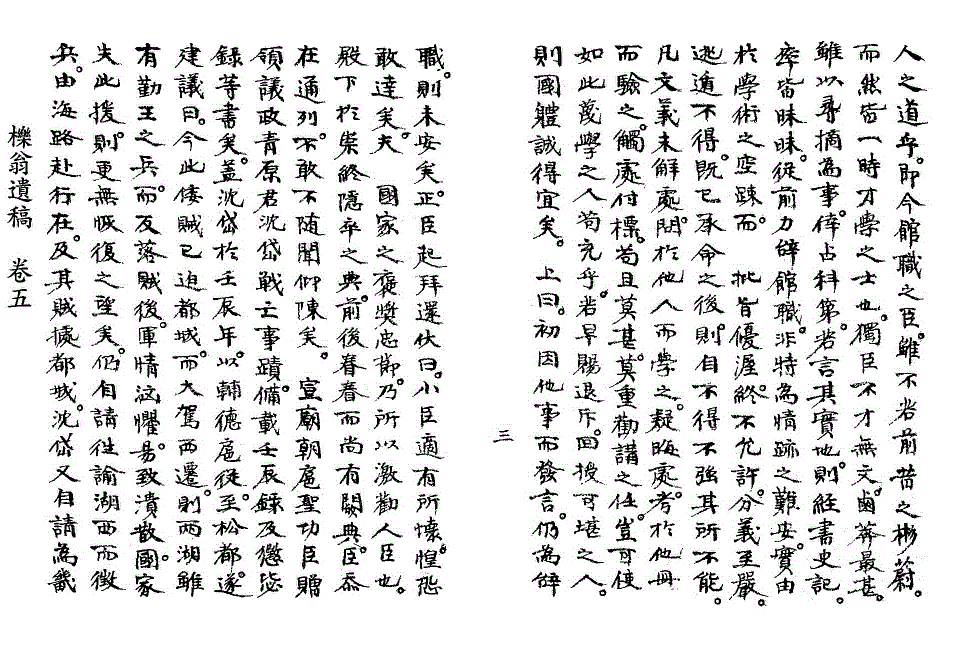 人之道乎。即今馆职之臣。虽不若前昔之彬蔚。而然皆一时才学之士也。独臣不才无文。卤莽最甚。虽以寻摘为事。倖占科第。若言其实地。则经书史记。率皆昧昧。从前力辞馆职。非特为情迹之难安。实由于学术之空疏。而 批旨优渥。终不允许。分义至严。逃遁不得。既已承命之后。则自不得不强其所不能。凡文义未解处。问于他人而学之。疑晦处。考于他册而验之。触处付标。苟且莫甚。莫重劝讲之任。岂可使如此蔑学之人苟充乎。若早赐退斥。回授可堪之人。则国体诚得宜矣。 上曰。初因他事而发言。仍为辞职。则未安矣。正臣起拜还伏曰。小臣适有所怀。惶恐敢达矣。夫 国家之褒奖忠节。乃所以激劝人臣也。殿下于崇终隐卒之典。前后眷眷而尚有阙典。臣忝在迩列。不敢不随闻仰陈矣。 宣庙朝扈圣功臣赠领议政青原君沈岱战亡事迹。备载壬辰录及惩毖录等书矣。盖沈岱于壬辰年。以辅德扈从。至松都。遂建议曰。今此倭贼已迫都城。而大驾西迁。则两湖虽有勤王之兵。而反落贼后。军情汹惧。易致溃散。国家失此援。则更无恢复之望矣。仍自请往谕湖西而徵兵。由海路赴行在。及其贼据都城。沈岱又自请为畿
人之道乎。即今馆职之臣。虽不若前昔之彬蔚。而然皆一时才学之士也。独臣不才无文。卤莽最甚。虽以寻摘为事。倖占科第。若言其实地。则经书史记。率皆昧昧。从前力辞馆职。非特为情迹之难安。实由于学术之空疏。而 批旨优渥。终不允许。分义至严。逃遁不得。既已承命之后。则自不得不强其所不能。凡文义未解处。问于他人而学之。疑晦处。考于他册而验之。触处付标。苟且莫甚。莫重劝讲之任。岂可使如此蔑学之人苟充乎。若早赐退斥。回授可堪之人。则国体诚得宜矣。 上曰。初因他事而发言。仍为辞职。则未安矣。正臣起拜还伏曰。小臣适有所怀。惶恐敢达矣。夫 国家之褒奖忠节。乃所以激劝人臣也。殿下于崇终隐卒之典。前后眷眷而尚有阙典。臣忝在迩列。不敢不随闻仰陈矣。 宣庙朝扈圣功臣赠领议政青原君沈岱战亡事迹。备载壬辰录及惩毖录等书矣。盖沈岱于壬辰年。以辅德扈从。至松都。遂建议曰。今此倭贼已迫都城。而大驾西迁。则两湖虽有勤王之兵。而反落贼后。军情汹惧。易致溃散。国家失此援。则更无恢复之望矣。仍自请往谕湖西而徵兵。由海路赴行在。及其贼据都城。沈岱又自请为畿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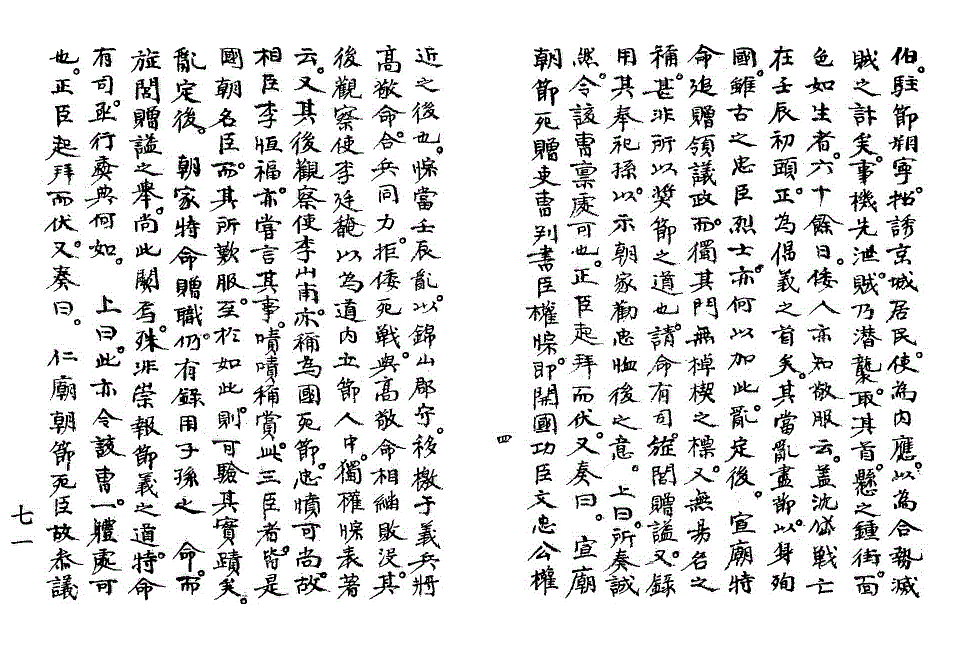 伯。驻节朔宁。招诱京城居民。使为内应。以为合势灭贼之计矣。事机先泄。贼乃潜袭。取其首。悬之钟街。面色如生者。六十馀日。倭人亦知敬服云。盖沈岱战亡在壬辰初头。正为倡义之首矣。其当乱尽节。以身殉国。虽古之忠臣烈士。亦何以加此。乱定后。 宣庙特命追赠领议政。而独其门无棹楔之标。又无易名之称。甚非所以奖节之道也。请命有司。㫌闾赠谥。又录用其奉祀孙。以示朝家劝忠恤后之意。 上曰。所奏诚然。令该曹禀处可也。正臣起拜而伏。又奏曰。 宣庙朝节死赠吏曹判书臣权悰。即开国功臣文忠公权近之后也。悰当壬辰乱。以锦山郡守。移檄于义兵将高敬命。合兵同力。拒倭死战。与高敬命相继败没。其后观察使李廷馣以为道内立节人中。独权悰表著云。又其后观察使李山甫。亦称为国死节。忠愤可尚。故相臣李恒福。亦尝言其事。啧啧称赏。此三臣者。皆是国朝名臣。而其所叹服。至于如此。则可验其实迹矣。乱定后。 朝家特命赠职。仍有录用子孙之 命。而㫌闾赠谥之举。尚此阙焉。殊非崇报节义之道。特命有司。亟行彝典何如。 上曰。此亦令该曹。一体处可也。正臣起拜而伏。又奏曰。 仁庙朝节死臣故参议
伯。驻节朔宁。招诱京城居民。使为内应。以为合势灭贼之计矣。事机先泄。贼乃潜袭。取其首。悬之钟街。面色如生者。六十馀日。倭人亦知敬服云。盖沈岱战亡在壬辰初头。正为倡义之首矣。其当乱尽节。以身殉国。虽古之忠臣烈士。亦何以加此。乱定后。 宣庙特命追赠领议政。而独其门无棹楔之标。又无易名之称。甚非所以奖节之道也。请命有司。㫌闾赠谥。又录用其奉祀孙。以示朝家劝忠恤后之意。 上曰。所奏诚然。令该曹禀处可也。正臣起拜而伏。又奏曰。 宣庙朝节死赠吏曹判书臣权悰。即开国功臣文忠公权近之后也。悰当壬辰乱。以锦山郡守。移檄于义兵将高敬命。合兵同力。拒倭死战。与高敬命相继败没。其后观察使李廷馣以为道内立节人中。独权悰表著云。又其后观察使李山甫。亦称为国死节。忠愤可尚。故相臣李恒福。亦尝言其事。啧啧称赏。此三臣者。皆是国朝名臣。而其所叹服。至于如此。则可验其实迹矣。乱定后。 朝家特命赠职。仍有录用子孙之 命。而㫌闾赠谥之举。尚此阙焉。殊非崇报节义之道。特命有司。亟行彝典何如。 上曰。此亦令该曹。一体处可也。正臣起拜而伏。又奏曰。 仁庙朝节死臣故参议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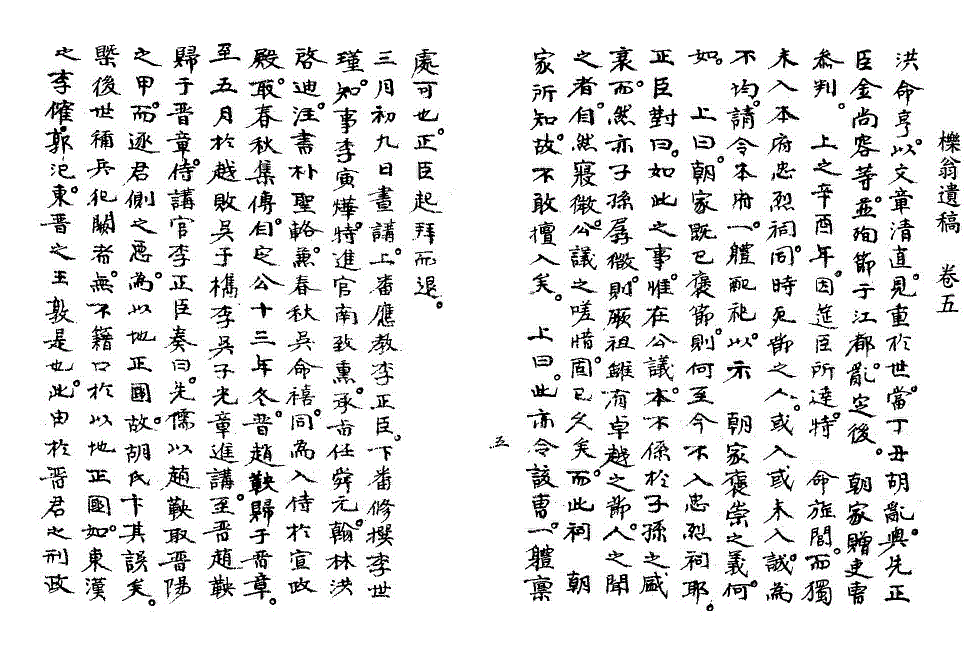 洪命亨。以文章清直。见重于世。当丁丑胡乱。与先正臣金尚容等。并殉节于江都。乱定后。 朝家赠吏曹参判。 上之辛酉年。因筵臣所达。特 命㫌闾。而独未入本府忠烈祠。同时死节之人。或入或未入。诚为不均。请令本府。一体配祀。以示 朝家褒崇之义。何如。 上曰。朝家既已褒节。则何至今不入忠烈祠耶。正臣对曰。如此之事。惟在公议。本不系于子孙之盛衰。而然亦子孙孱微。则厥祖虽有卓越之节。人之闻之者。自然寝微。公议之嗟惜。固已久矣。而此祠 朝家所知。故不敢擅入矣。 上曰。此亦令该曹。一体禀处可也。正臣起拜而退。
洪命亨。以文章清直。见重于世。当丁丑胡乱。与先正臣金尚容等。并殉节于江都。乱定后。 朝家赠吏曹参判。 上之辛酉年。因筵臣所达。特 命㫌闾。而独未入本府忠烈祠。同时死节之人。或入或未入。诚为不均。请令本府。一体配祀。以示 朝家褒崇之义。何如。 上曰。朝家既已褒节。则何至今不入忠烈祠耶。正臣对曰。如此之事。惟在公议。本不系于子孙之盛衰。而然亦子孙孱微。则厥祖虽有卓越之节。人之闻之者。自然寝微。公议之嗟惜。固已久矣。而此祠 朝家所知。故不敢擅入矣。 上曰。此亦令该曹。一体禀处可也。正臣起拜而退。三月初九日昼讲。上番应教李正臣。下番修撰李世瑾。知事李寅烨。特进官南致熏。承旨任舜元。翰林洪启迪。注书朴圣辂。兼春秋吴命禧。同为入侍于宣政殿。取春秋集传。自定公十三年冬。晋赵鞅归于晋章。至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吴子光章进讲。至晋赵鞅归于晋章。侍讲官李正臣奏曰。先儒以赵鞅取晋阳之甲。而逐君侧之恶。为以地正国。故胡氏卞其误矣。槩后世称兵犯阙者。无不籍口于以地正国。如东汉之李傕,郭汜。东晋之王敦是也。此由于晋君之刑政
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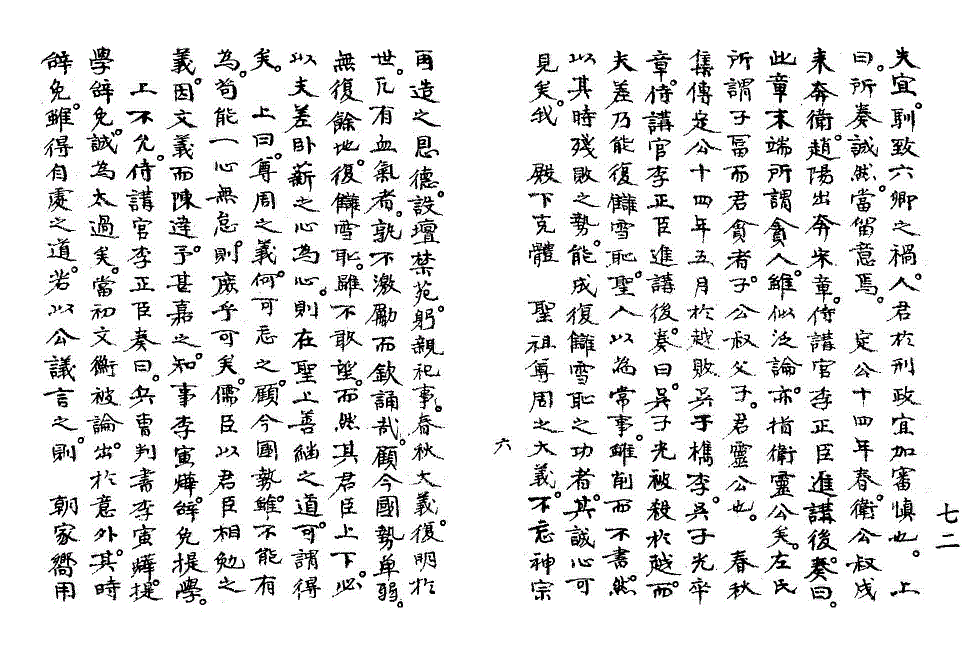 失宜。驯致六卿之祸。人君于刑政宜加审慎也。 上曰。所奏诚然。当留意焉。 定公十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章。侍讲官李正臣进讲后。奏曰。此章末端所谓贪人。虽似泛论。亦指卫灵公矣。左氏所谓子富而君贪者。子公叔父子。君灵公也。 春秋集传定公十四年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吴子光卒章。侍讲官李正臣进讲后。奏曰。吴子光被杀于越。而夫差乃能复雠雪耻。圣人以为常事。虽削而不书。然以其时残败之势。能成复雠雪耻之功者。其诚心可见矣。我 殿下克体 圣祖尊周之大义。不忘神宗再造之恩德。设坛禁苑。躬亲祀事。春秋大义。复明于世。凡有血气者。孰不激励而钦诵哉。顾今国势单弱。无复馀地。复雠雪耻。虽不敢望。而然其君臣上下。必以夫差卧薪之心为心。则在圣上善继之道。可谓得矣。 上曰。尊周之义。何可忘之。顾今国势。虽不能有为。苟能一心无怠。则庶乎可矣。儒臣以君臣相勉之义。因文义而陈达。予甚嘉之。知事李寅烨。辞免提学。 上不允。侍讲官李正臣奏曰。兵曹判书李寅烨。提学辞免。诚为太过矣。当初文衡被论。出于意外。其时辞免。虽得自处之道。若以公议言之。则 朝家向用
失宜。驯致六卿之祸。人君于刑政宜加审慎也。 上曰。所奏诚然。当留意焉。 定公十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章。侍讲官李正臣进讲后。奏曰。此章末端所谓贪人。虽似泛论。亦指卫灵公矣。左氏所谓子富而君贪者。子公叔父子。君灵公也。 春秋集传定公十四年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吴子光卒章。侍讲官李正臣进讲后。奏曰。吴子光被杀于越。而夫差乃能复雠雪耻。圣人以为常事。虽削而不书。然以其时残败之势。能成复雠雪耻之功者。其诚心可见矣。我 殿下克体 圣祖尊周之大义。不忘神宗再造之恩德。设坛禁苑。躬亲祀事。春秋大义。复明于世。凡有血气者。孰不激励而钦诵哉。顾今国势单弱。无复馀地。复雠雪耻。虽不敢望。而然其君臣上下。必以夫差卧薪之心为心。则在圣上善继之道。可谓得矣。 上曰。尊周之义。何可忘之。顾今国势。虽不能有为。苟能一心无怠。则庶乎可矣。儒臣以君臣相勉之义。因文义而陈达。予甚嘉之。知事李寅烨。辞免提学。 上不允。侍讲官李正臣奏曰。兵曹判书李寅烨。提学辞免。诚为太过矣。当初文衡被论。出于意外。其时辞免。虽得自处之道。若以公议言之。则 朝家向用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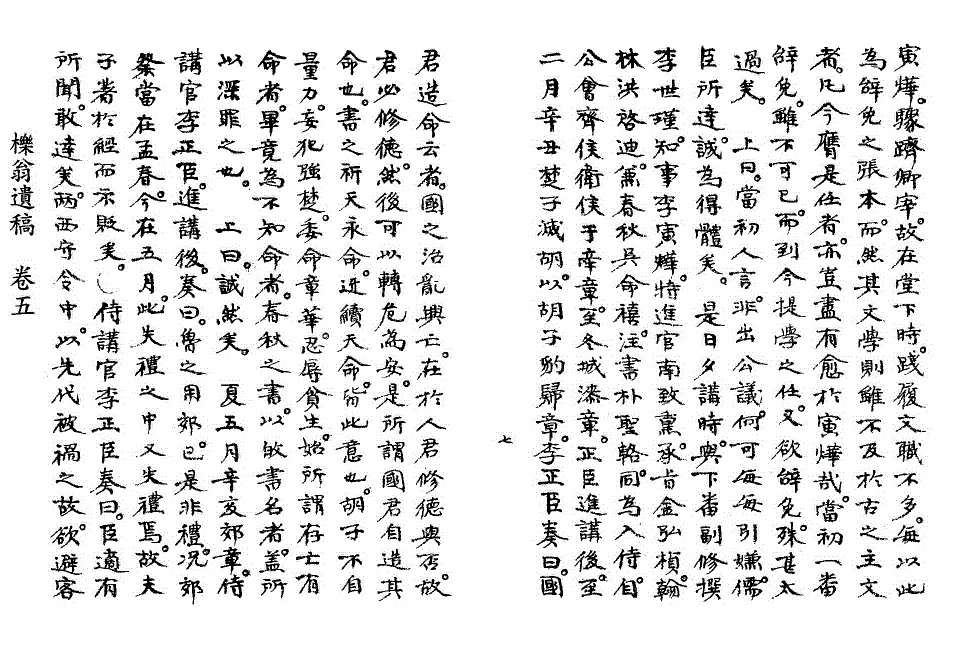 寅烨。骤跻卿宰。故在堂下时。践履文职不多。每以此为辞免之张本。而然其文学则虽不及于古之主文者。凡今膺是任者。亦岂尽有愈于寅烨哉。当初一番辞免。虽不可已。而到今提学之任。又欲辞免。殊甚太过矣。 上曰。当初人言。非出公议。何可每每引嫌。儒臣所达。诚为得体矣。○是日夕讲时。与下番副修撰李世瑾。知事李寅烨。特进官南致熏。承旨金弘桢。翰林洪启迪。兼春秋吴命禧。注书朴圣辂。同为入侍。自公会齐侯卫侯于牵章。至冬城漆章。正臣进讲后。至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章。李正臣奏曰。国君造命云者。国之治乱兴亡。在于人君修德与否。故君必修德。然后可以转危为安。是所谓国君自造其命也。书之祈天永命。迓续天命。皆此意也。胡子不自量力。妄犯强楚。委命章华。忍辱贪生。始所谓存亡有命者。毕竟为不知命者。春秋之书。以敀书名者。盖所以深罪之也。 上曰。诚然矣。○夏五月辛亥郊章。侍讲官李正臣。进讲后。奏曰。鲁之用郊。已是非礼。况郊祭当在孟春。今在五月。此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夫子著于经而示贬矣。○侍讲官李正臣奏曰。臣适有所闻。敢达矣。两西守令中。以先代被祸之故。欲避客
寅烨。骤跻卿宰。故在堂下时。践履文职不多。每以此为辞免之张本。而然其文学则虽不及于古之主文者。凡今膺是任者。亦岂尽有愈于寅烨哉。当初一番辞免。虽不可已。而到今提学之任。又欲辞免。殊甚太过矣。 上曰。当初人言。非出公议。何可每每引嫌。儒臣所达。诚为得体矣。○是日夕讲时。与下番副修撰李世瑾。知事李寅烨。特进官南致熏。承旨金弘桢。翰林洪启迪。兼春秋吴命禧。注书朴圣辂。同为入侍。自公会齐侯卫侯于牵章。至冬城漆章。正臣进讲后。至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章。李正臣奏曰。国君造命云者。国之治乱兴亡。在于人君修德与否。故君必修德。然后可以转危为安。是所谓国君自造其命也。书之祈天永命。迓续天命。皆此意也。胡子不自量力。妄犯强楚。委命章华。忍辱贪生。始所谓存亡有命者。毕竟为不知命者。春秋之书。以敀书名者。盖所以深罪之也。 上曰。诚然矣。○夏五月辛亥郊章。侍讲官李正臣。进讲后。奏曰。鲁之用郊。已是非礼。况郊祭当在孟春。今在五月。此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夫子著于经而示贬矣。○侍讲官李正臣奏曰。臣适有所闻。敢达矣。两西守令中。以先代被祸之故。欲避客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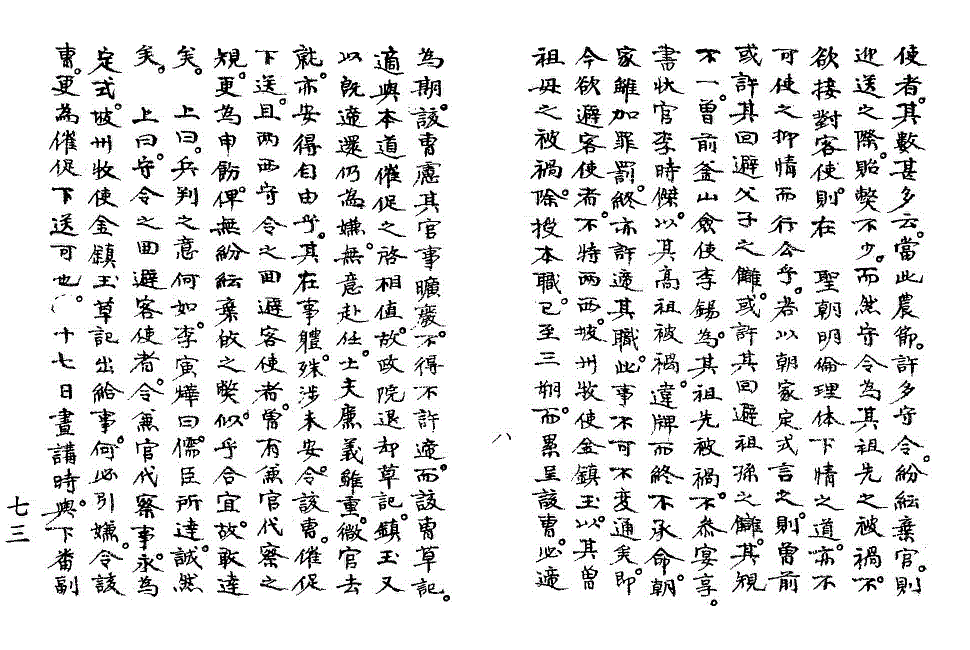 使者。其数甚多云。当此农节。许多守令。纷纭弃官。则迎送之际。贻弊不少。而然守令为其祖先之被祸。不欲接对客使。则在 圣朝明伦理体下情之道。亦不可使之抑情而行公乎。若以朝家定式言之。则曾前或许其回避父子之雠。或许其回避祖孙之雠。其规不一。曾前釜山佥使李锡。为其祖先被祸。不参宴享。书状官李时杰。以其高祖被祸。违牌而终不承命。朝家虽加罪罚。终亦许遆其职。此事不可不变通矣。即今欲避客使者。不特两西。坡州牧使金镇玉。以其曾祖母之被祸。除授本职。已至三朔。而累呈该曹。必遆为期。该曹虑其官事旷废。不得不许遆。而该曹草记。适与本道催促之启相值。故政院退却草记。镇玉又以既遆还仍为嫌。无意赴任。士夫廉义虽重。微官去就。亦安得自由乎。其在事体。殊涉未安。令该曹。催促下送。且两西守令之回避客使者。曾有兼官代察之规。更为申饬。俾无纷纭弃敀之弊。似乎合宜。故敢达矣。 上曰。兵判之意何如。李寅烨曰。儒臣所达。诚然矣。 上曰。守令之回避客使者。令兼官代察事。永为定式。坡州牧使金镇玉草记出给事。何必引嫌。令该曹。更为催促下送可也。○十七日昼讲时。与下番副
使者。其数甚多云。当此农节。许多守令。纷纭弃官。则迎送之际。贻弊不少。而然守令为其祖先之被祸。不欲接对客使。则在 圣朝明伦理体下情之道。亦不可使之抑情而行公乎。若以朝家定式言之。则曾前或许其回避父子之雠。或许其回避祖孙之雠。其规不一。曾前釜山佥使李锡。为其祖先被祸。不参宴享。书状官李时杰。以其高祖被祸。违牌而终不承命。朝家虽加罪罚。终亦许遆其职。此事不可不变通矣。即今欲避客使者。不特两西。坡州牧使金镇玉。以其曾祖母之被祸。除授本职。已至三朔。而累呈该曹。必遆为期。该曹虑其官事旷废。不得不许遆。而该曹草记。适与本道催促之启相值。故政院退却草记。镇玉又以既遆还仍为嫌。无意赴任。士夫廉义虽重。微官去就。亦安得自由乎。其在事体。殊涉未安。令该曹。催促下送。且两西守令之回避客使者。曾有兼官代察之规。更为申饬。俾无纷纭弃敀之弊。似乎合宜。故敢达矣。 上曰。兵判之意何如。李寅烨曰。儒臣所达。诚然矣。 上曰。守令之回避客使者。令兼官代察事。永为定式。坡州牧使金镇玉草记出给事。何必引嫌。令该曹。更为催促下送可也。○十七日昼讲时。与下番副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4H 页
 修撰李世瑾。知事崔锡恒。特进官尹就商。承旨韩配夏。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南一明。兼春秋赵之重。入侍于宣政殿。上番侍讲官李正臣。取春秋集传三十六篇。自哀公元年春王正月。止敀二家而不取也。读讲讫。至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章。奏曰。鲁定公四年十一月。蔡侯以吴子楚人战柏举。楚师败绩云。胡传所谓柏举者。即指此而言也。○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章。奏曰。胡传所谓大夫祭五祀之五祀。见礼记月令。孟春祀户。孟夏祀灶。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门。孟冬祀行。是也。中央是未月末。而在火金之间。居一岁之中。雨霤之后。因名室中为中霤。亦土神也。○至秋齐侯,卫侯伐晋章。奏曰。周室东迁以后。礼乐征伐。不得自天子出。王道尽矣。惟五霸迭作。尊周室而攘夷狄。主盟奉命。禁暴救乱。则其亦有功于王室矣。今者晋为霸主。而齐卫以列国。无所忌惮。合从擅伐。则霸统又亡。春秋之变。至是而极矣。此夫子所以揭此而特书。昭示后人者也。 上曰。诚然矣。○至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章。奏曰。所谓漷东田沂西田云者。非谓井田之田也。何休注以为田多邑小曰田。意者。漷东沂西。似应田野广而邑治小。故以田而
修撰李世瑾。知事崔锡恒。特进官尹就商。承旨韩配夏。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南一明。兼春秋赵之重。入侍于宣政殿。上番侍讲官李正臣。取春秋集传三十六篇。自哀公元年春王正月。止敀二家而不取也。读讲讫。至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章。奏曰。鲁定公四年十一月。蔡侯以吴子楚人战柏举。楚师败绩云。胡传所谓柏举者。即指此而言也。○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章。奏曰。胡传所谓大夫祭五祀之五祀。见礼记月令。孟春祀户。孟夏祀灶。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门。孟冬祀行。是也。中央是未月末。而在火金之间。居一岁之中。雨霤之后。因名室中为中霤。亦土神也。○至秋齐侯,卫侯伐晋章。奏曰。周室东迁以后。礼乐征伐。不得自天子出。王道尽矣。惟五霸迭作。尊周室而攘夷狄。主盟奉命。禁暴救乱。则其亦有功于王室矣。今者晋为霸主。而齐卫以列国。无所忌惮。合从擅伐。则霸统又亡。春秋之变。至是而极矣。此夫子所以揭此而特书。昭示后人者也。 上曰。诚然矣。○至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章。奏曰。所谓漷东田沂西田云者。非谓井田之田也。何休注以为田多邑小曰田。意者。漷东沂西。似应田野广而邑治小。故以田而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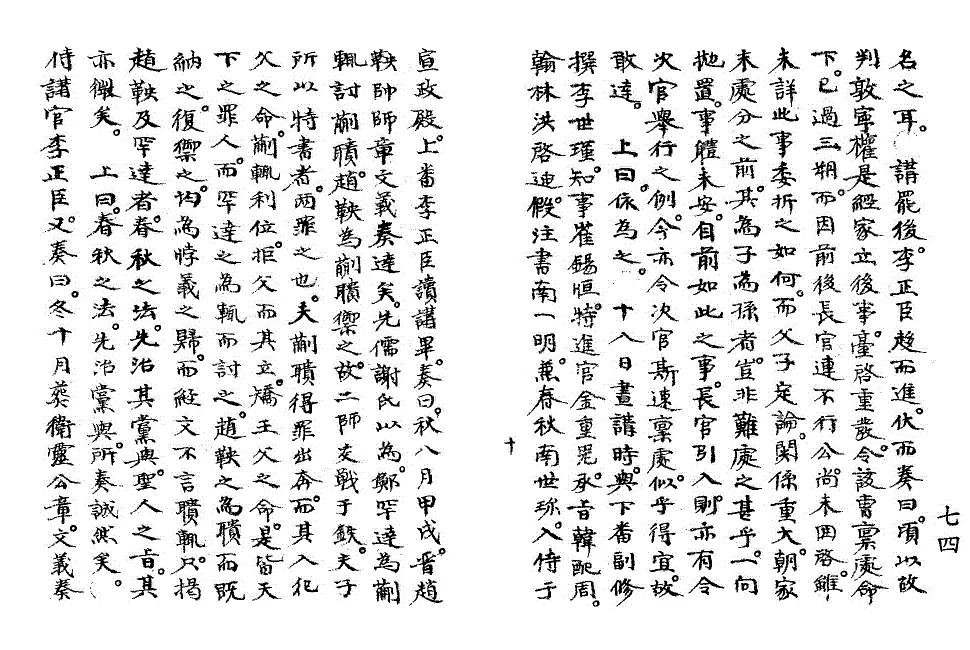 名之耳。○讲罢后。李正臣趍而进。伏而奏曰。顷以故判敦宁权是经家立后事。台启重发。令该曹禀处命下。已过三朔。而因前后长官连不行公。尚未回启。虽未详此事委折之如何。而父子定论。关系重大。朝家未处分之前。其为子为孙者。岂非难处之甚乎。一向抛置。事体未安。自前如此之事。长官引入。则亦有令次官举行之例。今亦令次官斯速禀处。似乎得宜。故敢达。 上曰。依为之。○十八日昼讲时。与下番副修撰李世瑾。知事崔锡恒。特进官金重器。承旨韩配周。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南一明。兼春秋南世珍。入侍于宣政殿。上番李正臣读讲毕。奏曰。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章文义奏达矣。先儒谢氏以为。郑罕达为蒯辄讨蒯聩。赵鞅为蒯聩御之。故二师交战于铁。夫子所以特书者。两罪之也。夫蒯聩得罪出奔。而其入犯父之命。蒯辄利位。拒父而其立。矫王父之命。是皆天下之罪人。而罕达之为辄而讨之。赵鞅之为聩而既纳之。复御之。均为悖义之归。而经文不言聩辄。只揭赵鞅及罕达者。春秋之法。先治其党与。圣人之旨。其亦微矣。 上曰。春秋之法。先治党与。所奏诚然矣。○侍讲官李正臣。又奏曰。冬十月葬卫灵公章。文义奏
名之耳。○讲罢后。李正臣趍而进。伏而奏曰。顷以故判敦宁权是经家立后事。台启重发。令该曹禀处命下。已过三朔。而因前后长官连不行公。尚未回启。虽未详此事委折之如何。而父子定论。关系重大。朝家未处分之前。其为子为孙者。岂非难处之甚乎。一向抛置。事体未安。自前如此之事。长官引入。则亦有令次官举行之例。今亦令次官斯速禀处。似乎得宜。故敢达。 上曰。依为之。○十八日昼讲时。与下番副修撰李世瑾。知事崔锡恒。特进官金重器。承旨韩配周。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南一明。兼春秋南世珍。入侍于宣政殿。上番李正臣读讲毕。奏曰。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章文义奏达矣。先儒谢氏以为。郑罕达为蒯辄讨蒯聩。赵鞅为蒯聩御之。故二师交战于铁。夫子所以特书者。两罪之也。夫蒯聩得罪出奔。而其入犯父之命。蒯辄利位。拒父而其立。矫王父之命。是皆天下之罪人。而罕达之为辄而讨之。赵鞅之为聩而既纳之。复御之。均为悖义之归。而经文不言聩辄。只揭赵鞅及罕达者。春秋之法。先治其党与。圣人之旨。其亦微矣。 上曰。春秋之法。先治党与。所奏诚然矣。○侍讲官李正臣。又奏曰。冬十月葬卫灵公章。文义奏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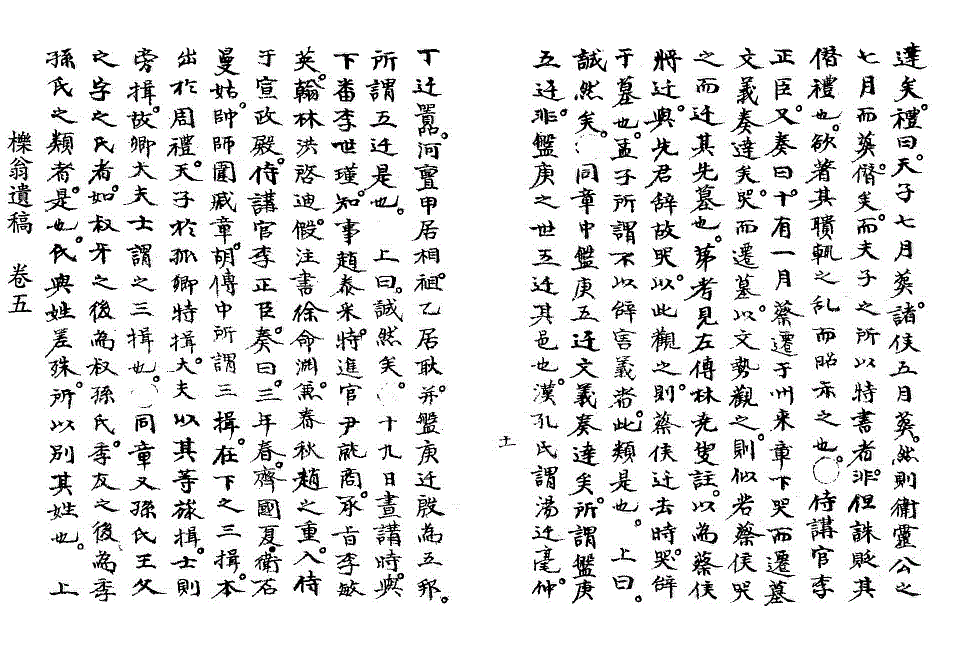 达矣。礼曰。天子七月葬。诸侯五月葬。然则卫灵公之七月而葬。僭矣。而夫子之所以特书者。非但诛贬其僭礼也。欲著其聩辄之乱而昭示之也。○侍讲官李正臣。又奏曰。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章下哭而迁墓文义奏达矣。哭而迁墓。以文势观之。则似若蔡侯哭之而迁其先墓也。第考见左传林尧叟注。以为蔡侯将迁。与先君辞故哭。以此观之。则蔡侯迁去时。哭辞于墓也。孟子所谓不以辞害义者。此类是也。 上曰。诚然矣。○同章中盘庚五迁文义奏达矣。所谓盘庚五迁。非盘庚之世五迁其邑也。汉孔氏谓汤迁毫。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盘庚迁殷为五邦。所谓五迁是也。 上曰。诚然矣。○十九日昼讲时。与下番李世瑾。知事赵泰采。特进官尹就商。承旨李敏英。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徐命渊。兼春秋赵之重。入侍于宣政殿。侍讲官李正臣。奏曰。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章。胡传中所谓三揖。在下之三揖。本出于周礼。天子于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则旁揖。故卿大夫士谓之三揖也。○同章又孙氏王父之字之氏者。如叔牙之后为叔孙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之类者。是也。氏与姓差殊。所以别其姓也。 上
达矣。礼曰。天子七月葬。诸侯五月葬。然则卫灵公之七月而葬。僭矣。而夫子之所以特书者。非但诛贬其僭礼也。欲著其聩辄之乱而昭示之也。○侍讲官李正臣。又奏曰。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章下哭而迁墓文义奏达矣。哭而迁墓。以文势观之。则似若蔡侯哭之而迁其先墓也。第考见左传林尧叟注。以为蔡侯将迁。与先君辞故哭。以此观之。则蔡侯迁去时。哭辞于墓也。孟子所谓不以辞害义者。此类是也。 上曰。诚然矣。○同章中盘庚五迁文义奏达矣。所谓盘庚五迁。非盘庚之世五迁其邑也。汉孔氏谓汤迁毫。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盘庚迁殷为五邦。所谓五迁是也。 上曰。诚然矣。○十九日昼讲时。与下番李世瑾。知事赵泰采。特进官尹就商。承旨李敏英。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徐命渊。兼春秋赵之重。入侍于宣政殿。侍讲官李正臣。奏曰。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章。胡传中所谓三揖。在下之三揖。本出于周礼。天子于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则旁揖。故卿大夫士谓之三揖也。○同章又孙氏王父之字之氏者。如叔牙之后为叔孙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之类者。是也。氏与姓差殊。所以别其姓也。 上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5L 页
 曰。诚然矣。○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章。胡传末端选择其祖宗而尊事之说。窃有未晚者。盖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见于经典。皆有明文。而朱子以商周之制。为是。程子亦论庙制。而以太祖,太宗。谓百世不迁。以此论之。则胡氏所论与商周之制程朱之论。未免径庭矣。臣无学术。见识瞢昧。胡氏宋之大贤也。虽不敢遽谓其论之或涉于可疑。而然亦既有程朱定论。则取舍恐不难矣。如此等处。关系甚重。 乙览之际。不宜放过也。 上曰。选择祖宗之说。 予览时亦以为未安矣。今儒臣之意又如此。所奏诚为得当矣。▦四年二月盗杀蔡侯申章。胡传末端。有苏辙以谓求名而不得之说。公孙翩。是弑君之贼。辙之言。岂非可骇之甚乎。胡氏贬斥诚宜矣。臣于正月十六日 召对时。入侍于熙政堂。节酌通编答程允夫书中。朱子贬斥苏黄门书三端。臣尝进讲。 圣明想或记有之矣。盖苏黄门。即辙也。辙之学。本于佛老。故其发为文辞者。类皆诡谲。害于义理者甚多。朱子以为其心术昏蔽。惟以闳衍之辞。捭阖之辨。眩世俗之耳目。今于论春秋之说。益验朱子之不我欺矣。夫文章。大关世教。即今 圣明在上。导率得宜。则群下学术之真。心术之
曰。诚然矣。○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章。胡传末端选择其祖宗而尊事之说。窃有未晚者。盖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见于经典。皆有明文。而朱子以商周之制。为是。程子亦论庙制。而以太祖,太宗。谓百世不迁。以此论之。则胡氏所论与商周之制程朱之论。未免径庭矣。臣无学术。见识瞢昧。胡氏宋之大贤也。虽不敢遽谓其论之或涉于可疑。而然亦既有程朱定论。则取舍恐不难矣。如此等处。关系甚重。 乙览之际。不宜放过也。 上曰。选择祖宗之说。 予览时亦以为未安矣。今儒臣之意又如此。所奏诚为得当矣。▦四年二月盗杀蔡侯申章。胡传末端。有苏辙以谓求名而不得之说。公孙翩。是弑君之贼。辙之言。岂非可骇之甚乎。胡氏贬斥诚宜矣。臣于正月十六日 召对时。入侍于熙政堂。节酌通编答程允夫书中。朱子贬斥苏黄门书三端。臣尝进讲。 圣明想或记有之矣。盖苏黄门。即辙也。辙之学。本于佛老。故其发为文辞者。类皆诡谲。害于义理者甚多。朱子以为其心术昏蔽。惟以闳衍之辞。捭阖之辨。眩世俗之耳目。今于论春秋之说。益验朱子之不我欺矣。夫文章。大关世教。即今 圣明在上。导率得宜。则群下学术之真。心术之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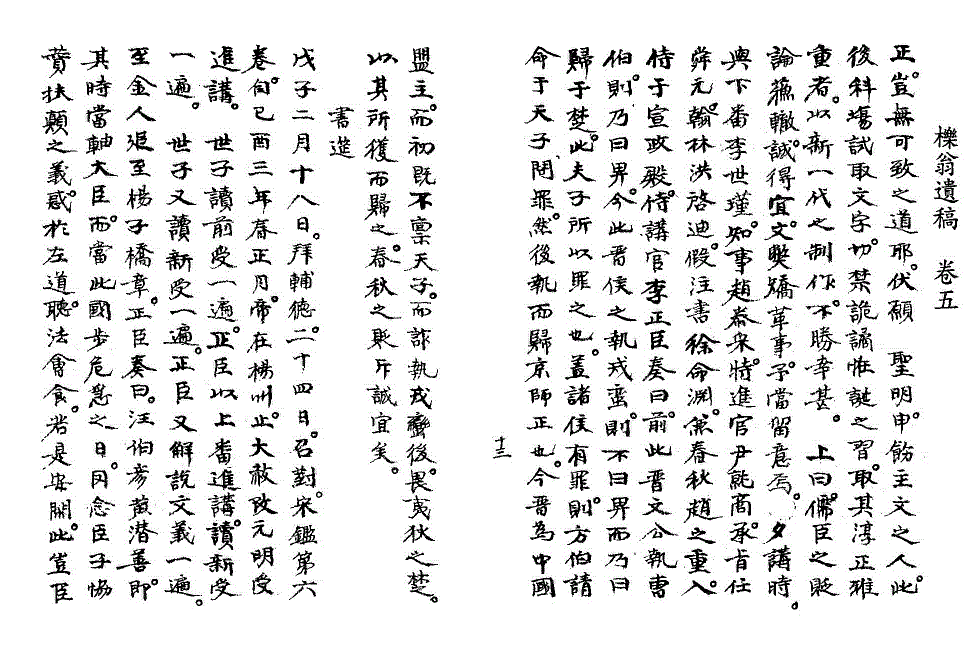 正。岂无可致之道耶。伏愿 圣明。申饬主文之人。此后科场试取文字。切禁诡谲怪诞之习。取其淳正雅重者。以新一代之制作。不胜幸甚。 上曰。儒臣之贬论苏辙。诚得宜。文弊矫革事。予当留意焉。○夕讲时。与下番李世瑾。知事赵泰采。特进官尹就商。承旨任舜元。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徐命渊。兼春秋赵之重。入侍于宣政殿。侍讲官李正臣奏曰。前此晋文公执曹伯。则乃曰畀。今此晋侯之执戎蛮。则不曰畀而乃曰归于楚。此夫子所以罪之也。盖诸侯有罪。则方伯请命于天子问罪。然后执而归京师正也。今晋为中国盟主。而初既不禀天子。而诈执戎蛮后。畏夷狄之楚。以其所获而归之。春秋之贬斥诚宜矣。
正。岂无可致之道耶。伏愿 圣明。申饬主文之人。此后科场试取文字。切禁诡谲怪诞之习。取其淳正雅重者。以新一代之制作。不胜幸甚。 上曰。儒臣之贬论苏辙。诚得宜。文弊矫革事。予当留意焉。○夕讲时。与下番李世瑾。知事赵泰采。特进官尹就商。承旨任舜元。翰林洪启迪。假注书徐命渊。兼春秋赵之重。入侍于宣政殿。侍讲官李正臣奏曰。前此晋文公执曹伯。则乃曰畀。今此晋侯之执戎蛮。则不曰畀而乃曰归于楚。此夫子所以罪之也。盖诸侯有罪。则方伯请命于天子问罪。然后执而归京师正也。今晋为中国盟主。而初既不禀天子。而诈执戎蛮后。畏夷狄之楚。以其所获而归之。春秋之贬斥诚宜矣。书筵
戊子二月十八日。拜辅德。二十四日。召对。宋鉴第六卷。自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在杨州。止大赦改元明受进讲。 世子读前受一遍。正臣以上番进讲。读新受一遍。 世子又读新受一遍。正臣又解说文义一遍。至金人追至杨子桥章。正臣奏曰。汪伯彦黄潜善。即其时当轴大臣。而当此国步危急之日。罔念臣子协赞扶颠之义。惑于左道。听法会食。若是安闲。此岂臣
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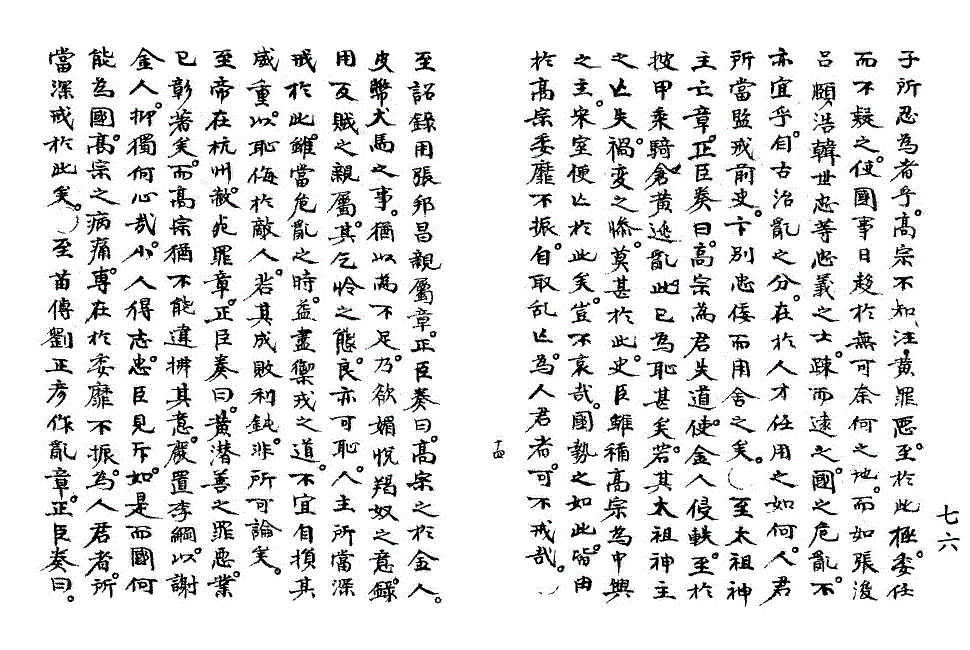 子所忍为者乎。高宗不知汪,黄罪恶。至于此极。委任而不疑之。使国事日趍于无可奈何之地。而如张浚吕颐浩韩世忠等忠义之士。疏而远之。国之危乱。不亦宜乎。自古治乱之分。在于人才任用之如何。人君所当监戒前史。卞别忠佞而用舍之矣。○至太祖神主亡章。正臣奏曰。高宗为君失道。使金人侵轶。至于披甲乘骑仓黄逃乱。此已为耻甚矣。若其太祖神主之亡失。祸变之惨。莫甚于此。史臣虽称高宗为中兴之主。宋室便亡于此矣。岂不哀哉。国势之如此。皆由于高宗委靡不振。自取乱亡。为人君者。可不戒哉。○至诏录用张邦昌亲属章。正臣奏曰。高宗之于金人。皮币犬马之事。犹以为不足。乃欲媚悦羯奴之意。录用反贼之亲属。其乞怜之态。良亦可耻。人主所当深戒于此。虽当危乱之时。益尽御戎之道。不宜自损其威重。以耻侮于敌人。若其成败利钝。非所可论矣。○至帝在杭州。赦死罪章。正臣奏曰。黄潜善之罪恶。业已彰著矣。而高宗犹不能违拂其意。废置李纲。以谢金人。抑独何心哉。小人得志。忠臣见斥。如是而国何能为国。高宗之病痛。专在于委靡不振。为人君者。所当深戒于此矣。○至苗传,刘正彦作乱章。正臣奏曰。
子所忍为者乎。高宗不知汪,黄罪恶。至于此极。委任而不疑之。使国事日趍于无可奈何之地。而如张浚吕颐浩韩世忠等忠义之士。疏而远之。国之危乱。不亦宜乎。自古治乱之分。在于人才任用之如何。人君所当监戒前史。卞别忠佞而用舍之矣。○至太祖神主亡章。正臣奏曰。高宗为君失道。使金人侵轶。至于披甲乘骑仓黄逃乱。此已为耻甚矣。若其太祖神主之亡失。祸变之惨。莫甚于此。史臣虽称高宗为中兴之主。宋室便亡于此矣。岂不哀哉。国势之如此。皆由于高宗委靡不振。自取乱亡。为人君者。可不戒哉。○至诏录用张邦昌亲属章。正臣奏曰。高宗之于金人。皮币犬马之事。犹以为不足。乃欲媚悦羯奴之意。录用反贼之亲属。其乞怜之态。良亦可耻。人主所当深戒于此。虽当危乱之时。益尽御戎之道。不宜自损其威重。以耻侮于敌人。若其成败利钝。非所可论矣。○至帝在杭州。赦死罪章。正臣奏曰。黄潜善之罪恶。业已彰著矣。而高宗犹不能违拂其意。废置李纲。以谢金人。抑独何心哉。小人得志。忠臣见斥。如是而国何能为国。高宗之病痛。专在于委靡不振。为人君者。所当深戒于此矣。○至苗传,刘正彦作乱章。正臣奏曰。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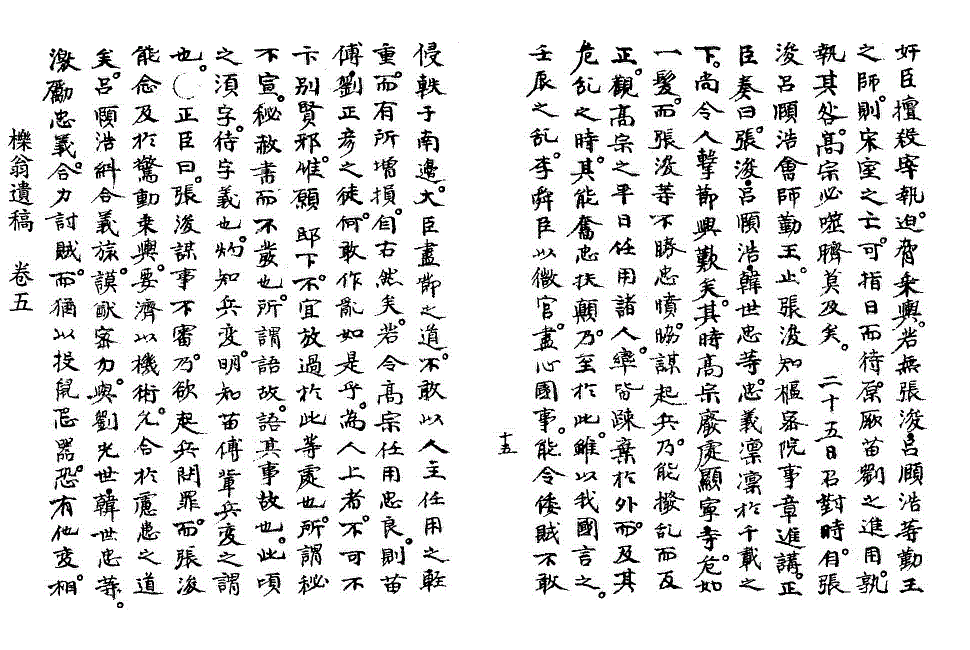 奸臣擅杀宰执。迫胁乘舆。若无张浚,吕颐浩等勤王之师。则宋室之亡。可指日而待。原厥苗,刘之进用。孰执其咎。高宗必噬脐莫及矣。○二十五日召对时。自张浚吕颐浩会师勤王。止张浚知枢密院事章进讲。正臣奏曰。张浚,吕颐浩,韩世忠等。忠义凛凛于千载之下。尚令人击节兴叹矣。其时高宗废处显宁寺。危如一发。而张浚等不胜忠愤。协谋起兵。乃能拨乱而反正。观高宗之平日任用诸人。率皆疏弃于外。而及其危乱之时。其能奋忠扶颠。乃至于此。虽以我国言之。壬辰之乱。李舜臣以微官。尽心国事。能令倭贼不敢侵轶于南边。大臣尽节之道。不敢以人主任用之轻重而有所增损。自古然矣。若令高宗任用忠良。则苗傅,刘正彦之徒。何敢作乱如是乎。为人上者。不可不卞别贤邪。唯愿邸下。不宜放过于此等处也。所谓秘不宣。秘赦书而不发也。所谓语故。语其事故也。此顷之须字。待字义也。灼知兵变。明知苗傅辈兵变之谓也。○正臣曰。张浚谋事不审。乃欲起兵问罪。而张浚能念及于惊动乘舆。要济以机术。允合于虑患之道矣。吕颐浩纠合义旅。谟猷密勿。与刘光世,韩世忠等。激励忠义。合力讨贼。而犹以投鼠忌器。恐有他变。相
奸臣擅杀宰执。迫胁乘舆。若无张浚,吕颐浩等勤王之师。则宋室之亡。可指日而待。原厥苗,刘之进用。孰执其咎。高宗必噬脐莫及矣。○二十五日召对时。自张浚吕颐浩会师勤王。止张浚知枢密院事章进讲。正臣奏曰。张浚,吕颐浩,韩世忠等。忠义凛凛于千载之下。尚令人击节兴叹矣。其时高宗废处显宁寺。危如一发。而张浚等不胜忠愤。协谋起兵。乃能拨乱而反正。观高宗之平日任用诸人。率皆疏弃于外。而及其危乱之时。其能奋忠扶颠。乃至于此。虽以我国言之。壬辰之乱。李舜臣以微官。尽心国事。能令倭贼不敢侵轶于南边。大臣尽节之道。不敢以人主任用之轻重而有所增损。自古然矣。若令高宗任用忠良。则苗傅,刘正彦之徒。何敢作乱如是乎。为人上者。不可不卞别贤邪。唯愿邸下。不宜放过于此等处也。所谓秘不宣。秘赦书而不发也。所谓语故。语其事故也。此顷之须字。待字义也。灼知兵变。明知苗傅辈兵变之谓也。○正臣曰。张浚谋事不审。乃欲起兵问罪。而张浚能念及于惊动乘舆。要济以机术。允合于虑患之道矣。吕颐浩纠合义旅。谟猷密勿。与刘光世,韩世忠等。激励忠义。合力讨贼。而犹以投鼠忌器。恐有他变。相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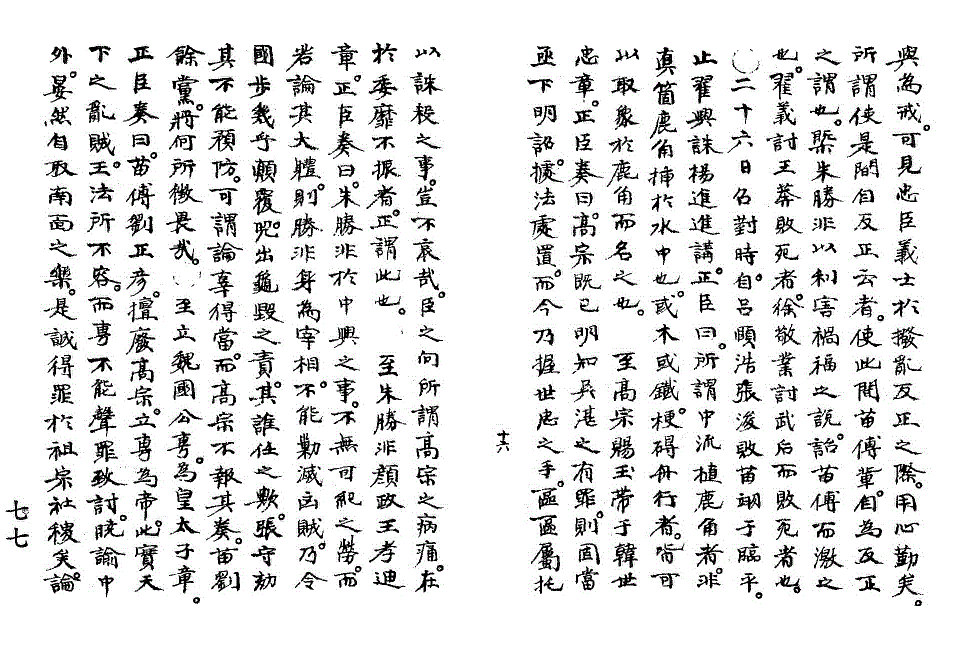 与为戒。可见忠臣义士于拨乱反正之际。用心勤矣。所谓使是间自反正云者。使此间苗傅辈。自为反正之谓也。槩朱胜非以利害祸福之说。诒苗傅而激之也。翟义讨王莽败死者。徐敬业讨武后而败死者也。○二十六日召对时。自吕颐浩,张浚败苗翊于临平。止翟兴诛杨进进讲。正臣曰。所谓中流植鹿角者。非真个鹿角插于水中也。或木或铁。梗碍舟行者。皆可以取象于鹿角而名之也。○至高宗赐玉带于韩世忠章。正臣奏曰。高宗既已明知吴湛之有罪。则固当亟下明诏。据法处置。而今乃握世忠之手。区区属托以诛杀之事。岂不哀哉。臣之向所谓高宗之病痛。在于委靡不振者。正谓此也。○至朱胜非颜政王孝迪章。正臣奏曰。朱胜非于中兴之事。不无可纪之劳。而若论其大体。则胜非身为宰相。不能剿灭凶贼。乃令国步几乎颠覆。兕出龟毁之责。其谁任之欤。张守劾其不能预防。可谓论辜得当。而高宗不报其奏。苗,刘馀党。将何所徵畏哉。○至立魏国公敷。为皇太子章。正臣奏曰。苗傅,刘正彦。擅废高宗。立敷为帝。此实天下之乱贼。王法所不容。而敷不能声罪致讨。晓谕中外。晏然自取南面之乐。是诚得罪于祖宗社稷矣。论
与为戒。可见忠臣义士于拨乱反正之际。用心勤矣。所谓使是间自反正云者。使此间苗傅辈。自为反正之谓也。槩朱胜非以利害祸福之说。诒苗傅而激之也。翟义讨王莽败死者。徐敬业讨武后而败死者也。○二十六日召对时。自吕颐浩,张浚败苗翊于临平。止翟兴诛杨进进讲。正臣曰。所谓中流植鹿角者。非真个鹿角插于水中也。或木或铁。梗碍舟行者。皆可以取象于鹿角而名之也。○至高宗赐玉带于韩世忠章。正臣奏曰。高宗既已明知吴湛之有罪。则固当亟下明诏。据法处置。而今乃握世忠之手。区区属托以诛杀之事。岂不哀哉。臣之向所谓高宗之病痛。在于委靡不振者。正谓此也。○至朱胜非颜政王孝迪章。正臣奏曰。朱胜非于中兴之事。不无可纪之劳。而若论其大体。则胜非身为宰相。不能剿灭凶贼。乃令国步几乎颠覆。兕出龟毁之责。其谁任之欤。张守劾其不能预防。可谓论辜得当。而高宗不报其奏。苗,刘馀党。将何所徵畏哉。○至立魏国公敷。为皇太子章。正臣奏曰。苗傅,刘正彦。擅废高宗。立敷为帝。此实天下之乱贼。王法所不容。而敷不能声罪致讨。晓谕中外。晏然自取南面之乐。是诚得罪于祖宗社稷矣。论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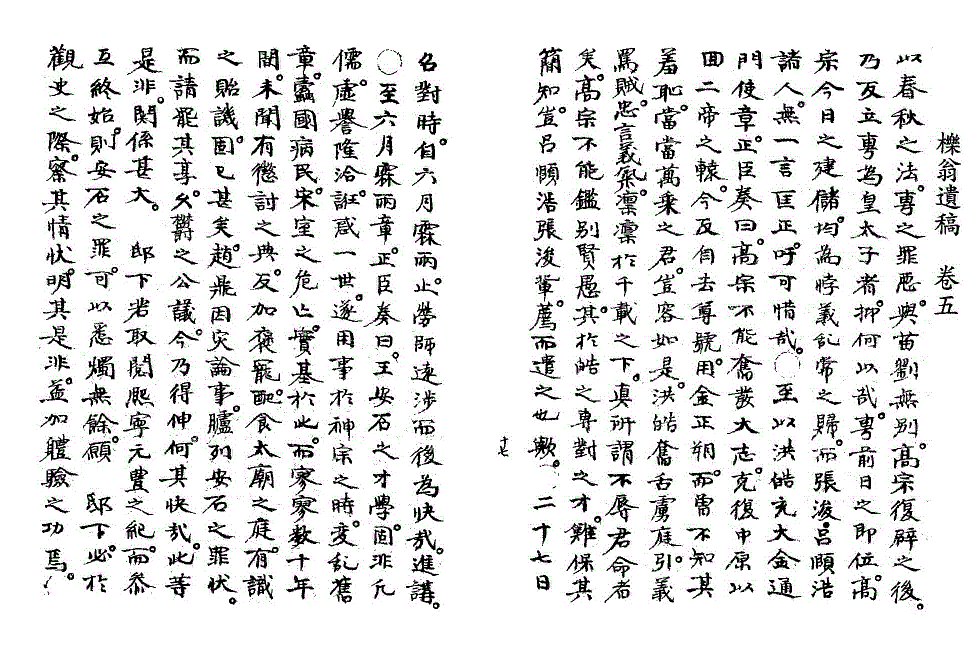 以春秋之法。敷之罪恶。与苗,刘无别。高宗复辟之后。乃反立敷为皇太子者。抑何以哉。敷前日之即位。高宗今日之建储。均为悖义乱常之归。而张浚,吕颐浩诸人。无一言匡正。吁可惜哉。○至以洪皓充大金通门使章。正臣奏曰。高宗不能奋发大志。克复中原以回二帝之辕。今反自去尊号。用金正朔。而曾不知其羞耻。当当万乘之君。岂容如是。洪皓奋舌虏庭。引义骂贼。忠言义气。凛凛于千载之下。真所谓不辱君命者矣。高宗不能鉴别贤愚。其于皓之专对之才。难保其简知。岂吕颐浩,张浚辈。荐而遣之也欤。○二十七日召对时。自六月霖雨。止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进讲。○至六月霖雨章。正臣奏曰。王安石之才学。固非凡儒。虚誉隆洽。诳惑一世。遂用事于神宗之时。变乱旧章。蠹国病民。宋室之危亡。实基于此。而寥寥数十年间。未闻有惩讨之典。反加褒宠。配食太庙之庭。有识之贻讥。固已甚矣。赵鼎因灾论事。胪列安石之罪状。而请罢其享。久郁之公议。今乃得伸。何其快哉。此等是非。关系甚大。 邸下若取阅熙宁,元礼之纪。而参互终始。则安石之罪。可以悉烛无馀。愿 邸下。必于观史之际。察其情状。明其是非。益加体验之功焉。○
以春秋之法。敷之罪恶。与苗,刘无别。高宗复辟之后。乃反立敷为皇太子者。抑何以哉。敷前日之即位。高宗今日之建储。均为悖义乱常之归。而张浚,吕颐浩诸人。无一言匡正。吁可惜哉。○至以洪皓充大金通门使章。正臣奏曰。高宗不能奋发大志。克复中原以回二帝之辕。今反自去尊号。用金正朔。而曾不知其羞耻。当当万乘之君。岂容如是。洪皓奋舌虏庭。引义骂贼。忠言义气。凛凛于千载之下。真所谓不辱君命者矣。高宗不能鉴别贤愚。其于皓之专对之才。难保其简知。岂吕颐浩,张浚辈。荐而遣之也欤。○二十七日召对时。自六月霖雨。止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进讲。○至六月霖雨章。正臣奏曰。王安石之才学。固非凡儒。虚誉隆洽。诳惑一世。遂用事于神宗之时。变乱旧章。蠹国病民。宋室之危亡。实基于此。而寥寥数十年间。未闻有惩讨之典。反加褒宠。配食太庙之庭。有识之贻讥。固已甚矣。赵鼎因灾论事。胪列安石之罪状。而请罢其享。久郁之公议。今乃得伸。何其快哉。此等是非。关系甚大。 邸下若取阅熙宁,元礼之纪。而参互终始。则安石之罪。可以悉烛无馀。愿 邸下。必于观史之际。察其情状。明其是非。益加体验之功焉。○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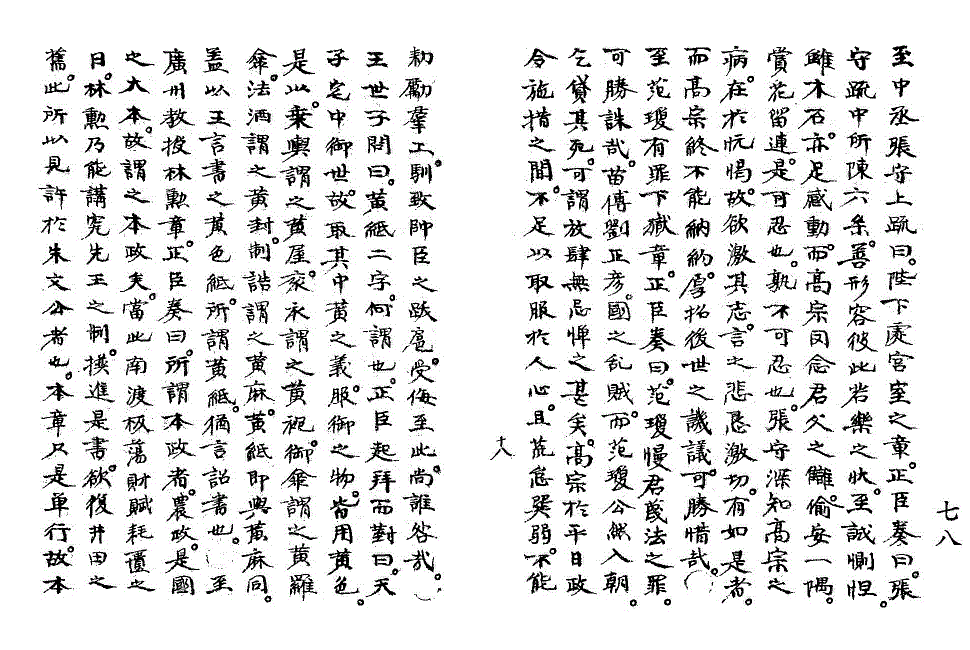 至中丞张守上疏曰。陛下处宫室之章。正臣奏曰。张守疏中所陈六条。善形容彼此若乐之状。至诚恻怛。虽木石。亦足感动。而高宗罔念君父之雠。偷安一隅。赏花留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张守深知高宗之病。在于忨愒。故欲激其志。言之悲恳激切。有如是者。而高宗终不能纳约。厚招后世之讥议。可胜惜哉。○至范琼有罪下狱章。正臣奏曰。范琼慢君蔑法之罪。可胜诛哉。苗傅,刘正彦。国之乱贼。而范琼公然入朝。乞贷其死。可谓放肆无忌惮之甚矣。高宗于平日政令施措之间。不足以取服于人心。且荒怠巽弱。不能敕励群工。驯致帅臣之跋扈。受侮至此。尚谁咎哉。○王世子问曰。黄纸二字。何谓也。正臣起拜而对曰。天子宅中御世。故取其中黄之义。服御之物。皆用黄色。是以。乘舆谓之黄屋。衮衣谓之黄袍。御伞谓之黄罗伞。法酒谓之黄封。制诰谓之黄麻。黄纸即与黄麻同。盖以王言书之黄色纸。所谓黄纸。犹言诏书也。○至广州教授林勋章。正臣奏曰。所谓本政者。农政。是国之大本。故谓之本政矣。当此南渡板荡财赋耗匮之日。林勋乃能讲究先王之制。撰进是书。欲复井田之旧。此所以见许于朱文公者也。本章只是单行。故本
至中丞张守上疏曰。陛下处宫室之章。正臣奏曰。张守疏中所陈六条。善形容彼此若乐之状。至诚恻怛。虽木石。亦足感动。而高宗罔念君父之雠。偷安一隅。赏花留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张守深知高宗之病。在于忨愒。故欲激其志。言之悲恳激切。有如是者。而高宗终不能纳约。厚招后世之讥议。可胜惜哉。○至范琼有罪下狱章。正臣奏曰。范琼慢君蔑法之罪。可胜诛哉。苗傅,刘正彦。国之乱贼。而范琼公然入朝。乞贷其死。可谓放肆无忌惮之甚矣。高宗于平日政令施措之间。不足以取服于人心。且荒怠巽弱。不能敕励群工。驯致帅臣之跋扈。受侮至此。尚谁咎哉。○王世子问曰。黄纸二字。何谓也。正臣起拜而对曰。天子宅中御世。故取其中黄之义。服御之物。皆用黄色。是以。乘舆谓之黄屋。衮衣谓之黄袍。御伞谓之黄罗伞。法酒谓之黄封。制诰谓之黄麻。黄纸即与黄麻同。盖以王言书之黄色纸。所谓黄纸。犹言诏书也。○至广州教授林勋章。正臣奏曰。所谓本政者。农政。是国之大本。故谓之本政矣。当此南渡板荡财赋耗匮之日。林勋乃能讲究先王之制。撰进是书。欲复井田之旧。此所以见许于朱文公者也。本章只是单行。故本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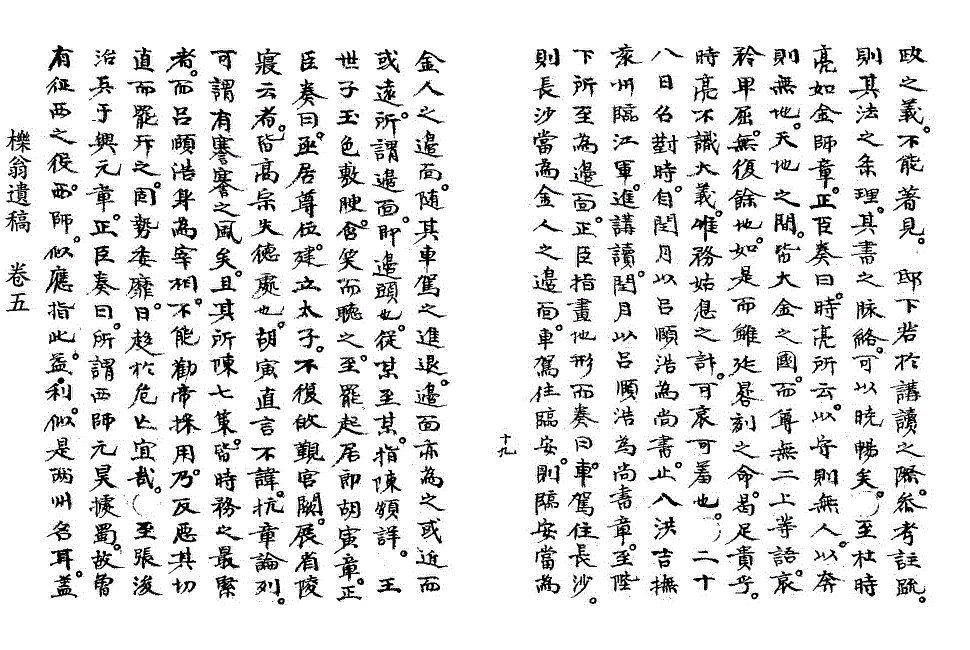 政之义。不能著见。 邸下若于讲读之际。参考注疏。则其法之条理。其书之脉络。可以晓畅矣。○至杜时亮如金师章。正臣奏曰。时亮所云。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等语。哀矜卑屈。无复馀地。如是而虽延晷刻之命。曷足贵乎。时亮不识大义。唯务姑息之计。可哀可羞也。○二十八日召对时。自闰月以吕颐浩为尚书。止入洪吉抚袁州临江军。进讲读。闰月以吕颐浩为尚书章。至陛下所至为边面。正臣指画地形而奏曰。车驾住长沙。则长沙当为金人之边面。车驾住临安。则临安当为金人之边面。随其车驾之进退。边面亦为之或近而或远。所谓边面。即边头也。从某至某。指陈颇详。 王世子玉色敷腴。含笑而听之。至罢起居郎胡寅章。正臣奏曰。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复敀觐宫阙。展省陵寝云者。皆高宗失德处也。胡寅直言不讳。抗章论列。可谓有謇謇之风矣。且其所陈七策。皆时务之最紧者。而吕颐浩身为宰相。不能劝帝采用。乃反恶其切直而罢斥之。固势委靡。日趍于危亡宜哉。○至张浚治兵于兴元章。正臣奏曰。所谓西师元昊据蜀。故曾有征西之役。西师。似应指此。益,利。似是两州名耳。盖
政之义。不能著见。 邸下若于讲读之际。参考注疏。则其法之条理。其书之脉络。可以晓畅矣。○至杜时亮如金师章。正臣奏曰。时亮所云。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等语。哀矜卑屈。无复馀地。如是而虽延晷刻之命。曷足贵乎。时亮不识大义。唯务姑息之计。可哀可羞也。○二十八日召对时。自闰月以吕颐浩为尚书。止入洪吉抚袁州临江军。进讲读。闰月以吕颐浩为尚书章。至陛下所至为边面。正臣指画地形而奏曰。车驾住长沙。则长沙当为金人之边面。车驾住临安。则临安当为金人之边面。随其车驾之进退。边面亦为之或近而或远。所谓边面。即边头也。从某至某。指陈颇详。 王世子玉色敷腴。含笑而听之。至罢起居郎胡寅章。正臣奏曰。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复敀觐宫阙。展省陵寝云者。皆高宗失德处也。胡寅直言不讳。抗章论列。可谓有謇謇之风矣。且其所陈七策。皆时务之最紧者。而吕颐浩身为宰相。不能劝帝采用。乃反恶其切直而罢斥之。固势委靡。日趍于危亡宜哉。○至张浚治兵于兴元章。正臣奏曰。所谓西师元昊据蜀。故曾有征西之役。西师。似应指此。益,利。似是两州名耳。盖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79L 页
 自蜀有西师之后。益,利等诸州。既以便宜从事。截取上供之物。及常平本货。而今已尽用。故张浚荐赵开理财。以办军国之需矣。今之各牙门。各营门。各道各邑之所谓料理殖货者。任事之人。徒怀希赏之心。剥割穷民。取给于公家。虽或有补于调度之万一。而民者。本也。财者。末也。岂有舍本取末。而利益于国家者乎。传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民之向背之分。实系于此。可不惧哉。愿 邸下深知领会。切勿放过于此等处。○二十九日召对时。自孙悟如金师。止惬朕朝夕慕念之意。进讲。○至赵鼎为御史中丞章。正臣奏曰。赵鼎所陈战守御三策。天下形势。实无过此。而高宗偷安岁月。无意兴复。虽有良平智谋之士。在帝左右。日进奇计。亦末如之何。良可惜哉。○至金兀朮入建康府章。正臣奏曰。杜充即当时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抚使也。其责任之重。倚毗之隆为如何。而不听岳飞之泣谏。武备疏虞。使建康根本之地。一朝瓦裂。其负国忘君之罪。固已难逃。而况流涎于兀朮之利诱。甘心于方昌之故事。屈膝雠庭。忍为降虏。而其通判杨邦乂。独不屈骂贼而死。其视杜充之失节。不啻天渊矣。高宗初若卞别忠佞。用
自蜀有西师之后。益,利等诸州。既以便宜从事。截取上供之物。及常平本货。而今已尽用。故张浚荐赵开理财。以办军国之需矣。今之各牙门。各营门。各道各邑之所谓料理殖货者。任事之人。徒怀希赏之心。剥割穷民。取给于公家。虽或有补于调度之万一。而民者。本也。财者。末也。岂有舍本取末。而利益于国家者乎。传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民之向背之分。实系于此。可不惧哉。愿 邸下深知领会。切勿放过于此等处。○二十九日召对时。自孙悟如金师。止惬朕朝夕慕念之意。进讲。○至赵鼎为御史中丞章。正臣奏曰。赵鼎所陈战守御三策。天下形势。实无过此。而高宗偷安岁月。无意兴复。虽有良平智谋之士。在帝左右。日进奇计。亦末如之何。良可惜哉。○至金兀朮入建康府章。正臣奏曰。杜充即当时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抚使也。其责任之重。倚毗之隆为如何。而不听岳飞之泣谏。武备疏虞。使建康根本之地。一朝瓦裂。其负国忘君之罪。固已难逃。而况流涎于兀朮之利诱。甘心于方昌之故事。屈膝雠庭。忍为降虏。而其通判杨邦乂。独不屈骂贼而死。其视杜充之失节。不啻天渊矣。高宗初若卞别忠佞。用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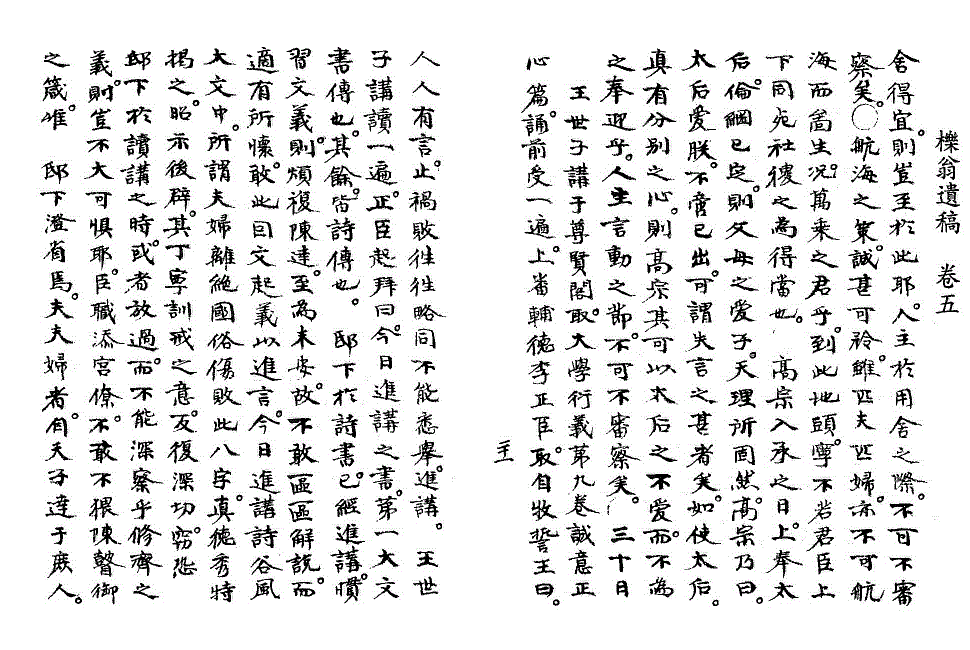 舍得宜。则岂至于此耶。人主于用舍之际。不可不审察矣。○航海之策。诚甚可矜。虽匹夫匹妇。亦不可航海而啚生。况万乘之君乎。到此地头。宁不若君臣上下同死社稷之为得当也。○高宗入承之日。上奉太后。伦纲已定。则父母之爱子。天理所固然。高宗乃曰。太后爱朕。不啻己出。可谓失言之甚者矣。如使太后。真有分别之心。则高宗其可以太后之不爱。而不为之奉迎乎。人主言动之节。不可不审察矣。○三十日 王世子讲于尊贤阁。取大学衍义第九卷诚意正心篇。诵前受一遍。上番辅德李正臣。取自牧誓王曰。人人有言。止祸败往往略同不能悉举。进讲。 王世子讲读一遍。正臣起拜曰。今日进讲之书。第一大文书传也。其馀。皆诗传也。 邸下于诗书。已经进讲。惯习文义。则烦复陈达。至为未安。故不敢区区解说。而适有所怀。敢此因文起义以进言。今日进讲诗谷风大文中。所谓夫妇离绝国俗伤败此八字。真德秀特揭之。昭示后辟。其丁宁训戒之意。反复深切。窃恐 邸下于读讲之时。或者放过。而不能深察乎修齐之义。则岂不大可惧耶。臣职添宫僚。不敢不猥陈𥌒御之箴。唯 邸下澄省焉。夫夫妇者。自天子达于庶人。
舍得宜。则岂至于此耶。人主于用舍之际。不可不审察矣。○航海之策。诚甚可矜。虽匹夫匹妇。亦不可航海而啚生。况万乘之君乎。到此地头。宁不若君臣上下同死社稷之为得当也。○高宗入承之日。上奉太后。伦纲已定。则父母之爱子。天理所固然。高宗乃曰。太后爱朕。不啻己出。可谓失言之甚者矣。如使太后。真有分别之心。则高宗其可以太后之不爱。而不为之奉迎乎。人主言动之节。不可不审察矣。○三十日 王世子讲于尊贤阁。取大学衍义第九卷诚意正心篇。诵前受一遍。上番辅德李正臣。取自牧誓王曰。人人有言。止祸败往往略同不能悉举。进讲。 王世子讲读一遍。正臣起拜曰。今日进讲之书。第一大文书传也。其馀。皆诗传也。 邸下于诗书。已经进讲。惯习文义。则烦复陈达。至为未安。故不敢区区解说。而适有所怀。敢此因文起义以进言。今日进讲诗谷风大文中。所谓夫妇离绝国俗伤败此八字。真德秀特揭之。昭示后辟。其丁宁训戒之意。反复深切。窃恐 邸下于读讲之时。或者放过。而不能深察乎修齐之义。则岂不大可惧耶。臣职添宫僚。不敢不猥陈𥌒御之箴。唯 邸下澄省焉。夫夫妇者。自天子达于庶人。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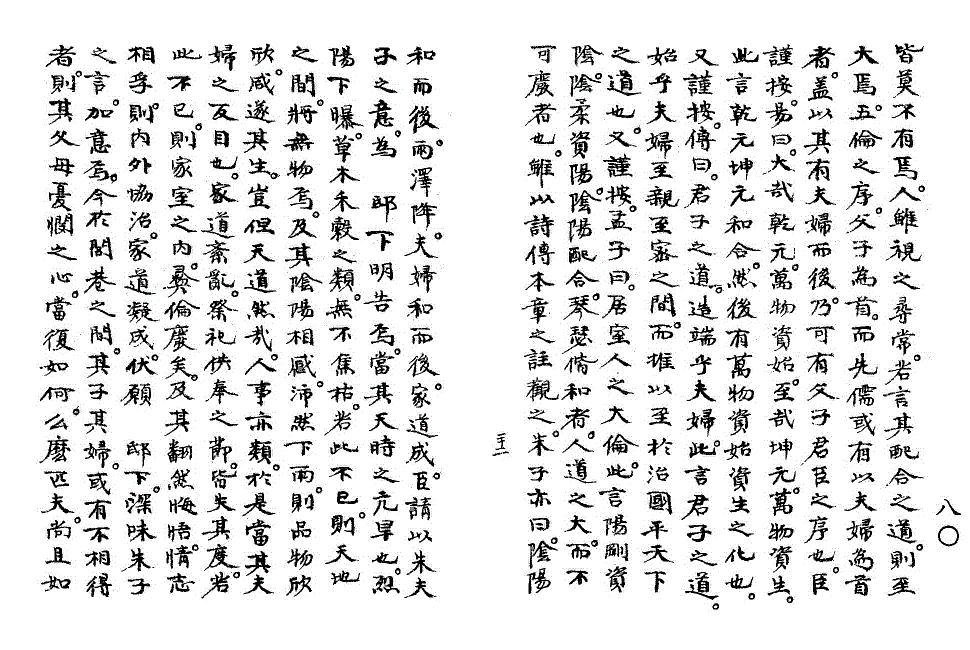 皆莫不有焉。人虽视之寻常。若言其配合之道。则至大焉。五伦之序。父子为首。而先儒或有以夫妇为首者。盖以其有夫妇而后。乃可有父子君臣之序也。臣谨按。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此言乾元坤元和合。然后有万物资始资生之化也。又谨按。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此言君子之道。始乎夫妇至亲至密之间。而推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之道也。又谨按。孟子曰。居室人之大伦。此言阳刚资阴。阴柔资阳。阴阳配合。琴瑟偕和者。人道之大。而不可废者也。虽以诗传本章之注观之。朱子亦曰。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臣请以朱夫子之意。为 邸下明告焉。当其天时之亢旱也。烈阳下曝。草木禾谷之类。无不焦枯。若此不已。则天地之间。将无物焉。及其阴阳相感。沛然下雨。则品物欣欣。咸遂其生。岂但天道然哉。人事亦类。于是当其夫妇之反目也。家道紊乱。祭祀供奉之节。皆失其度。若此不已。则家室之内。彝伦废矣。及其翻然悔悟。情志相孚。则内外协治。家道凝成。伏愿 邸下。深味朱子之言。加意焉。今于闾巷之间。其子其妇。或有不相得者。则其父母忧悯之心。当复如何。幺么匹夫。尚且如
皆莫不有焉。人虽视之寻常。若言其配合之道。则至大焉。五伦之序。父子为首。而先儒或有以夫妇为首者。盖以其有夫妇而后。乃可有父子君臣之序也。臣谨按。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此言乾元坤元和合。然后有万物资始资生之化也。又谨按。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此言君子之道。始乎夫妇至亲至密之间。而推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之道也。又谨按。孟子曰。居室人之大伦。此言阳刚资阴。阴柔资阳。阴阳配合。琴瑟偕和者。人道之大。而不可废者也。虽以诗传本章之注观之。朱子亦曰。阴阳和而后。雨泽降。夫妇和而后。家道成。臣请以朱夫子之意。为 邸下明告焉。当其天时之亢旱也。烈阳下曝。草木禾谷之类。无不焦枯。若此不已。则天地之间。将无物焉。及其阴阳相感。沛然下雨。则品物欣欣。咸遂其生。岂但天道然哉。人事亦类。于是当其夫妇之反目也。家道紊乱。祭祀供奉之节。皆失其度。若此不已。则家室之内。彝伦废矣。及其翻然悔悟。情志相孚。则内外协治。家道凝成。伏愿 邸下。深味朱子之言。加意焉。今于闾巷之间。其子其妇。或有不相得者。则其父母忧悯之心。当复如何。幺么匹夫。尚且如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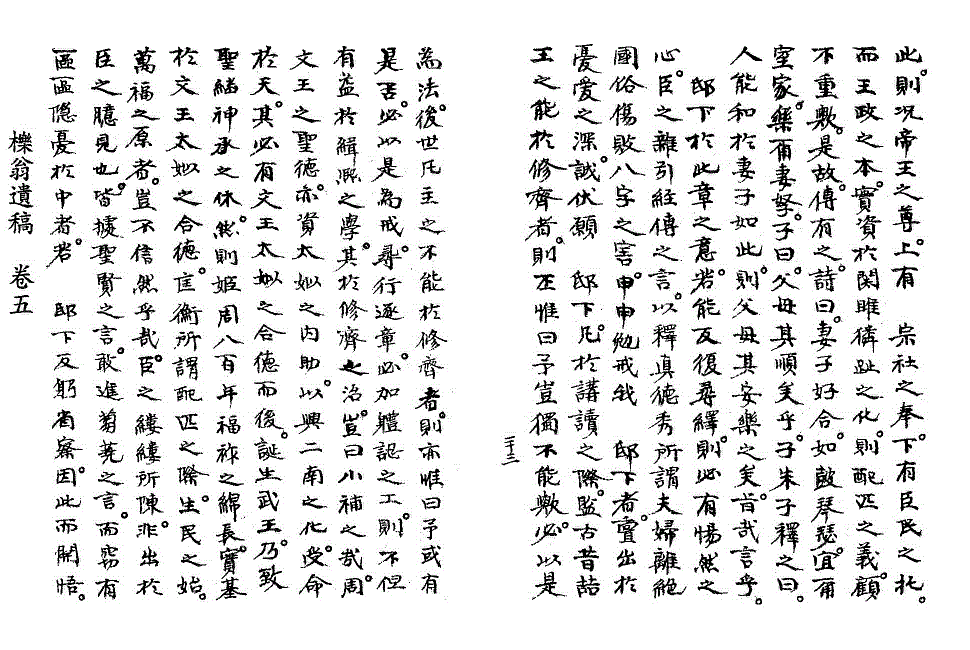 此。则况帝王之尊。上有 宗社之奉。下有臣民之托。而王政之本。实资于关雎獜趾之化。则配匹之义。顾不重欤。是故。传有之。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子朱子释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如此。则父母其安乐之矣。旨哉言乎。 邸下于此章之意。若能反复寻绎。则必有惕然之心。臣之杂引经传之言。以释真德秀所谓夫妇离绝国俗伤败八字之害。申申勉戒我 邸下者。亶出于忧爱之深。诚伏愿 邸下。凡于讲读之际。监古昔哲王之能于修齐者。则丕惟曰予岂独不能欤。必以是为法。后世凡主之不能于修齐者。则亦惟曰予或有是否。必以是为戒。寻行逐章。必加体认之工。则不但有益于缉熙之学。其于修齐之治。岂曰小补之哉。周文王之圣德。亦资太姒之内助。以兴二南之化。受命于天。其必有文王太姒之合德而后。诞生武王。乃致圣继神承之休。然则姬周八百年福祚之绵长。实基于文王太姒之合德。匡衡所谓配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者。岂不信然乎哉。臣之缕缕所陈。非出于臣之臆见也。皆据圣贤之言。敢进刍荛之言。而窃有区区隐忧于中者。若 邸下反躬省察。因此而开悟。
此。则况帝王之尊。上有 宗社之奉。下有臣民之托。而王政之本。实资于关雎獜趾之化。则配匹之义。顾不重欤。是故。传有之。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子朱子释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如此。则父母其安乐之矣。旨哉言乎。 邸下于此章之意。若能反复寻绎。则必有惕然之心。臣之杂引经传之言。以释真德秀所谓夫妇离绝国俗伤败八字之害。申申勉戒我 邸下者。亶出于忧爱之深。诚伏愿 邸下。凡于讲读之际。监古昔哲王之能于修齐者。则丕惟曰予岂独不能欤。必以是为法。后世凡主之不能于修齐者。则亦惟曰予或有是否。必以是为戒。寻行逐章。必加体认之工。则不但有益于缉熙之学。其于修齐之治。岂曰小补之哉。周文王之圣德。亦资太姒之内助。以兴二南之化。受命于天。其必有文王太姒之合德而后。诞生武王。乃致圣继神承之休。然则姬周八百年福祚之绵长。实基于文王太姒之合德。匡衡所谓配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者。岂不信然乎哉。臣之缕缕所陈。非出于臣之臆见也。皆据圣贤之言。敢进刍荛之言。而窃有区区隐忧于中者。若 邸下反躬省察。因此而开悟。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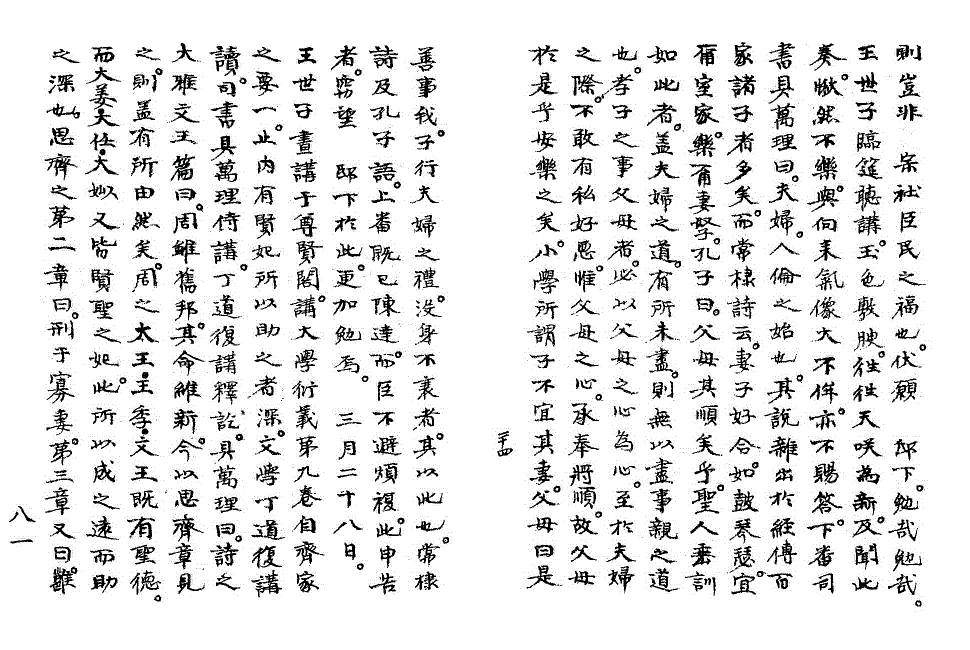 则岂非 宗社臣民之福也。伏愿 邸下。勉哉勉哉。王世子临筵听讲。玉色敷腴。往往天笑为新。及闻此奏。愀然不乐。与向来气像大不侔。亦不赐答。下番司书具万理曰。夫妇。人伦之始也。其说杂出于经传百家诸子者多矣。而常棣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圣人垂训如此者。盖夫妇之道。有所未尽。则无以尽事亲之道也。孝子之事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为心。至于夫妇之际。不敢有私好恶。惟父母之心。承奉将顺。故父母于是乎安乐之矣。小学所谓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没身不衰者。其以此也。常棣诗及孔子语。上番既已陈达。而臣不避烦复。此申告者。窃望 邸下于此。更加勉焉。○三月二十八日。 王世子昼讲于尊贤阁。讲大学衍义第九卷自齐家之要一。止内有贤妃所以助之者深。文学丁道复讲读。司书具万理侍讲。丁道复讲释讫。具万理曰。诗之大雅文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以思齐章见之。则盖有所由然矣。周之太王,王季,文王。既有圣德。而大姜,大任,大姒。又皆贤圣之妃。此所以成之远而助之深也。思齐之第二章曰。刑于寡妻。第三章又曰。雍
则岂非 宗社臣民之福也。伏愿 邸下。勉哉勉哉。王世子临筵听讲。玉色敷腴。往往天笑为新。及闻此奏。愀然不乐。与向来气像大不侔。亦不赐答。下番司书具万理曰。夫妇。人伦之始也。其说杂出于经传百家诸子者多矣。而常棣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圣人垂训如此者。盖夫妇之道。有所未尽。则无以尽事亲之道也。孝子之事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为心。至于夫妇之际。不敢有私好恶。惟父母之心。承奉将顺。故父母于是乎安乐之矣。小学所谓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没身不衰者。其以此也。常棣诗及孔子语。上番既已陈达。而臣不避烦复。此申告者。窃望 邸下于此。更加勉焉。○三月二十八日。 王世子昼讲于尊贤阁。讲大学衍义第九卷自齐家之要一。止内有贤妃所以助之者深。文学丁道复讲读。司书具万理侍讲。丁道复讲释讫。具万理曰。诗之大雅文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以思齐章见之。则盖有所由然矣。周之太王,王季,文王。既有圣德。而大姜,大任,大姒。又皆贤圣之妃。此所以成之远而助之深也。思齐之第二章曰。刑于寡妻。第三章又曰。雍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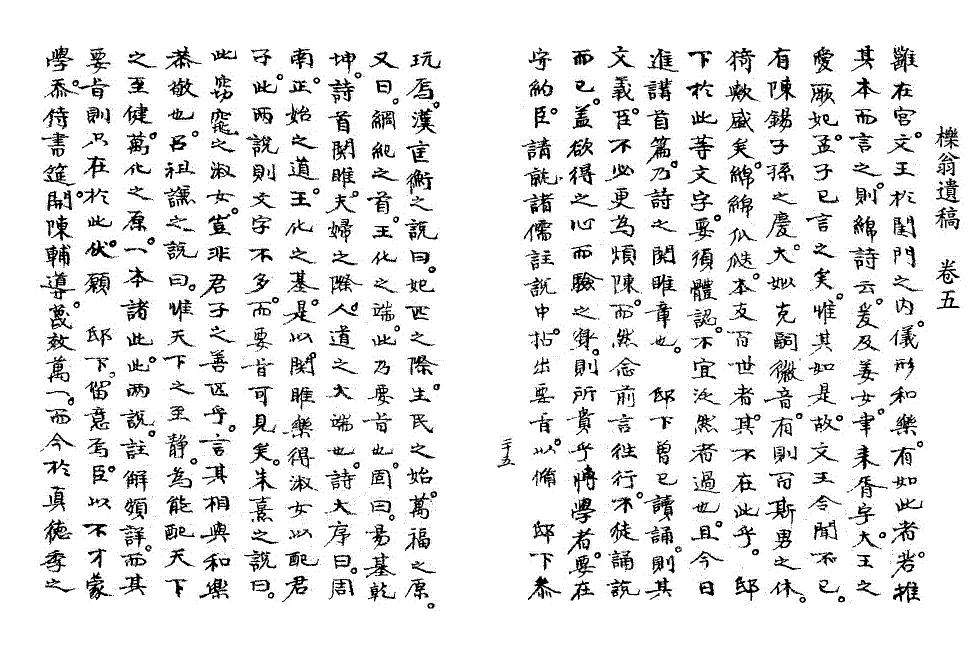 雍在宫。文王于闺门之内。仪形和乐。有如此者。若推其本而言之。则绵诗云。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大王之爱厥妃。孟子已言之矣。惟其如是。故文王令闻不已。有陈锡子孙之庆。大姒克嗣徽音。有则百斯男之休。猗欤盛矣。绵绵瓜瓞。本支百世者。其不在此乎。 邸下于此等文字。要须体认。不宜泛然者过也。且今日进讲首篇。乃诗之关雎章也。 邸下曾已读诵。则其文义。臣不必更为烦陈。而然念前言往行。不徒诵说而已。盖欲得之心而验之身。则所贵乎博学者。要在守约。臣请就诸儒注说中。拈出要旨。以备 邸下参玩焉。汉匡衡之说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又曰。纲纪之首。王化之端。此乃要旨也。固曰。易基乾坤。诗首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端也。诗大序曰。周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此两说则文字不多。而要旨可见矣。朱熹之说曰。此窃(一作窈)窕之淑女。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恭敬也。吕祖谦之说曰。惟天下之至静。为能配天下之至健。万化之原。一本诸此。此两说。注解颇详。而其要旨则只在于此。伏愿 邸下。留意焉。臣以不才蒙学。忝侍书筵。开陈辅导。蔑效万一。而今于真德季之
雍在宫。文王于闺门之内。仪形和乐。有如此者。若推其本而言之。则绵诗云。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大王之爱厥妃。孟子已言之矣。惟其如是。故文王令闻不已。有陈锡子孙之庆。大姒克嗣徽音。有则百斯男之休。猗欤盛矣。绵绵瓜瓞。本支百世者。其不在此乎。 邸下于此等文字。要须体认。不宜泛然者过也。且今日进讲首篇。乃诗之关雎章也。 邸下曾已读诵。则其文义。臣不必更为烦陈。而然念前言往行。不徒诵说而已。盖欲得之心而验之身。则所贵乎博学者。要在守约。臣请就诸儒注说中。拈出要旨。以备 邸下参玩焉。汉匡衡之说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又曰。纲纪之首。王化之端。此乃要旨也。固曰。易基乾坤。诗首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端也。诗大序曰。周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此两说则文字不多。而要旨可见矣。朱熹之说曰。此窃(一作窈)窕之淑女。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恭敬也。吕祖谦之说曰。惟天下之至静。为能配天下之至健。万化之原。一本诸此。此两说。注解颇详。而其要旨则只在于此。伏愿 邸下。留意焉。臣以不才蒙学。忝侍书筵。开陈辅导。蔑效万一。而今于真德季之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2L 页
 说。窃有所感叹于中者矣。宋理宗端平年间。真德秀辑成此书。进讲经筵。冀以感悟君心。则平生精力。尽在此中矣。其言曰关雎之义。诸儒尽之。惟 圣明参玩焉。所谓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灼然无疑矣。其所以条陈诸儒之说。勉戒其君。而诚意之勤勤恳恳。有如此者。臣于今日。乃敢以真德秀之望于其君者。望于邸下。邸下以为何如也。 王世子不即赐答。具万理曰。不任区区忧爱之忱。窃附古人敢有所仰达。而 邸下不赐下教。第切惶悚。 王世子下教曰。因文义陈达至此。当留心焉。具万理起而拜曰。 邸下之言及此。此宗社之福。臣民之庆也。臣敢不为国家贺也。如臣无似者。亦得以与有荣焉。伏不胜感幸之至。○闰三月初二日。 王世子昼讲于尊贤阁。讲大学衍义第九卷齐家之要一篇。汉显宗明德马皇后章下。真德秀按论说书。李真儒进言曰。臣极知惶恐。而窃有区区所怀。敢欲仰达。 王世子答曰。何事也。起拜而对曰。真德秀言马后之德有五。其一曰。忧皇嗣未广也。臣于此。窃有所感矣。 邸下春秋已踰弱冠。而尚未有嗣。臣民颙望之心。当复如何。顷者辅德李正臣。因文义有所缕缕陈达。司书具万理。又于日昨。因
说。窃有所感叹于中者矣。宋理宗端平年间。真德秀辑成此书。进讲经筵。冀以感悟君心。则平生精力。尽在此中矣。其言曰关雎之义。诸儒尽之。惟 圣明参玩焉。所谓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灼然无疑矣。其所以条陈诸儒之说。勉戒其君。而诚意之勤勤恳恳。有如此者。臣于今日。乃敢以真德秀之望于其君者。望于邸下。邸下以为何如也。 王世子不即赐答。具万理曰。不任区区忧爱之忱。窃附古人敢有所仰达。而 邸下不赐下教。第切惶悚。 王世子下教曰。因文义陈达至此。当留心焉。具万理起而拜曰。 邸下之言及此。此宗社之福。臣民之庆也。臣敢不为国家贺也。如臣无似者。亦得以与有荣焉。伏不胜感幸之至。○闰三月初二日。 王世子昼讲于尊贤阁。讲大学衍义第九卷齐家之要一篇。汉显宗明德马皇后章下。真德秀按论说书。李真儒进言曰。臣极知惶恐。而窃有区区所怀。敢欲仰达。 王世子答曰。何事也。起拜而对曰。真德秀言马后之德有五。其一曰。忧皇嗣未广也。臣于此。窃有所感矣。 邸下春秋已踰弱冠。而尚未有嗣。臣民颙望之心。当复如何。顷者辅德李正臣。因文义有所缕缕陈达。司书具万理。又于日昨。因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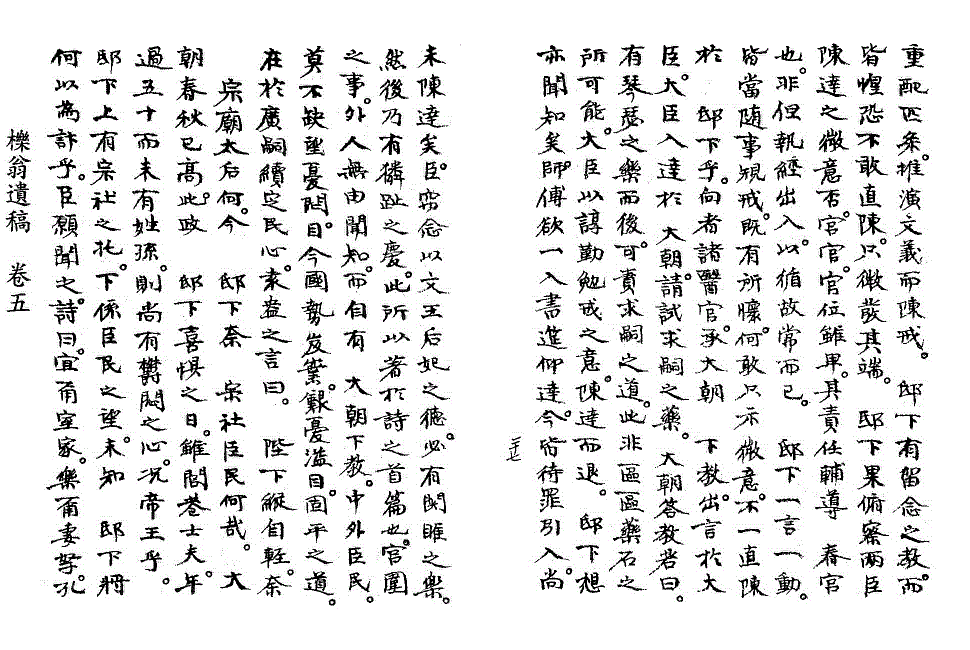 重配匹条。推演文义而陈戒。 邸下有留念之教。而皆惶恐不敢直陈。只微发其端。 邸下果俯察两臣陈达之微意否。宫官。官位虽卑。其责任辅导 春宫也。非但执经出入。以循故常而已。 邸下一言一动。皆当随事规戒。既有所怀。何敢只示微意。不一直陈于 邸下乎。向者诸医官。承大朝 下教。出言于大臣。大臣入达于 大朝。请试求嗣之药。 大朝答教若曰。有琴瑟之乐而后。可责求嗣之道。此非区区药石之所可能。大臣以谆勤勉戒之意。陈达而退。 邸下想亦闻知矣。师傅欲一入书筵仰达。今皆待罪引入。尚未陈达矣。臣窃念以文王后妃之德。必有关雎之乐。然后乃有獜趾之庆。此所以著于诗之首篇也。宫围之事。外人无由闻知。而自有 大朝下教。中外臣民。莫不缺望忧闷。目今国势岌嶪。艰忧溢目。固平之道。在于广嗣续定民心。袁盎之言曰。 陛下纵自轻。奈 宗庙太后何。今 邸下奈 宗社臣民何哉。 大朝春秋已高。此政 邸下喜惧之日。虽闾巷士夫。年过五十而未有姓孙。则尚有郁闷之心。况帝王乎。 邸下上有宗社之托。下系臣民之望。未知 邸下将何以为计乎。臣愿闻之。诗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孔
重配匹条。推演文义而陈戒。 邸下有留念之教。而皆惶恐不敢直陈。只微发其端。 邸下果俯察两臣陈达之微意否。宫官。官位虽卑。其责任辅导 春宫也。非但执经出入。以循故常而已。 邸下一言一动。皆当随事规戒。既有所怀。何敢只示微意。不一直陈于 邸下乎。向者诸医官。承大朝 下教。出言于大臣。大臣入达于 大朝。请试求嗣之药。 大朝答教若曰。有琴瑟之乐而后。可责求嗣之道。此非区区药石之所可能。大臣以谆勤勉戒之意。陈达而退。 邸下想亦闻知矣。师傅欲一入书筵仰达。今皆待罪引入。尚未陈达矣。臣窃念以文王后妃之德。必有关雎之乐。然后乃有獜趾之庆。此所以著于诗之首篇也。宫围之事。外人无由闻知。而自有 大朝下教。中外臣民。莫不缺望忧闷。目今国势岌嶪。艰忧溢目。固平之道。在于广嗣续定民心。袁盎之言曰。 陛下纵自轻。奈 宗庙太后何。今 邸下奈 宗社臣民何哉。 大朝春秋已高。此政 邸下喜惧之日。虽闾巷士夫。年过五十而未有姓孙。则尚有郁闷之心。况帝王乎。 邸下上有宗社之托。下系臣民之望。未知 邸下将何以为计乎。臣愿闻之。诗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孔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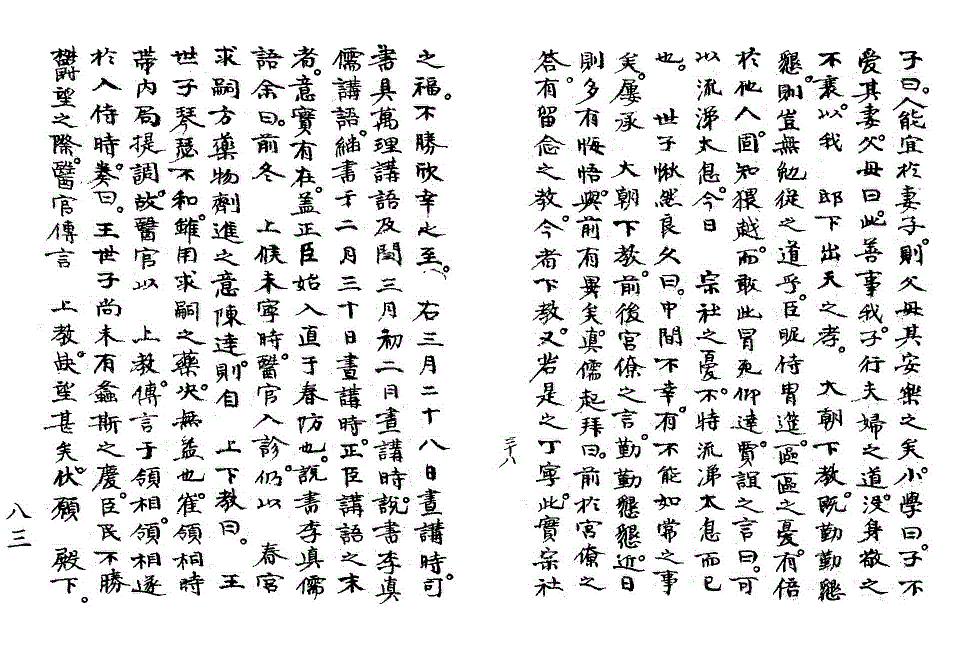 子曰。人能宜于妻子。则父母其安乐之矣。小学曰。子不爱其妻。父母曰。此善事我。子行夫妇之道。没身敬之不衰。以我 邸下出天之孝。 大朝下教。既勤勤恳恳。则岂无勉从之道乎。臣昵侍胄筵。区区之忧。有倍于他人。固知猥越。而敢此冒死仰达。贾谊之言曰。可以流涕太息。今日 宗社之忧。不特流涕太息而已也。 世子愀然良久曰。中间不幸。有不能如常之事矣。屡承 大朝下教。前后宫僚之言。勤勤恳恳。近日则多有悔悟。与前有异矣。真儒起拜曰。前于宫僚之答。有留念之教。今者下教。又若是之丁宁。此实宗社之福。不胜欣幸之至。○右三月二十八日昼讲时。司书具万理讲语及闰三月初二日昼讲时。说书李真儒讲语。继书于二月三十日昼讲时。正臣讲语之末者。意实有在。盖正臣始入直于春防也。说书李真儒语余曰。前冬 上候未宁时。医官入诊。仍以 春宫求嗣方药物剂进之意陈达。则自 上下教曰。 王世子琴瑟不和。虽用求嗣之药。决无益也。崔领相时带内局提调。故医官以 上教。传言于领相。领相遂于入侍时。奏曰。王世子尚未有螽斯之庆。臣民不胜郁望之际。医官传言 上教。缺望甚矣。伏愿 殿下。
子曰。人能宜于妻子。则父母其安乐之矣。小学曰。子不爱其妻。父母曰。此善事我。子行夫妇之道。没身敬之不衰。以我 邸下出天之孝。 大朝下教。既勤勤恳恳。则岂无勉从之道乎。臣昵侍胄筵。区区之忧。有倍于他人。固知猥越。而敢此冒死仰达。贾谊之言曰。可以流涕太息。今日 宗社之忧。不特流涕太息而已也。 世子愀然良久曰。中间不幸。有不能如常之事矣。屡承 大朝下教。前后宫僚之言。勤勤恳恳。近日则多有悔悟。与前有异矣。真儒起拜曰。前于宫僚之答。有留念之教。今者下教。又若是之丁宁。此实宗社之福。不胜欣幸之至。○右三月二十八日昼讲时。司书具万理讲语及闰三月初二日昼讲时。说书李真儒讲语。继书于二月三十日昼讲时。正臣讲语之末者。意实有在。盖正臣始入直于春防也。说书李真儒语余曰。前冬 上候未宁时。医官入诊。仍以 春宫求嗣方药物剂进之意陈达。则自 上下教曰。 王世子琴瑟不和。虽用求嗣之药。决无益也。崔领相时带内局提调。故医官以 上教。传言于领相。领相遂于入侍时。奏曰。王世子尚未有螽斯之庆。臣民不胜郁望之际。医官传言 上教。缺望甚矣。伏愿 殿下。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4H 页
 勉戒 春宫。俾令琴瑟合和。则岂非 宗社之福也。 上曰。予亦已屡度戒责。而不从予言。可闷。第当更为勉戒耳。领相兼世子师。故亦欲于入侍书筵时。勉戒 世子矣。意外被论于司谏尹世绥。方在引入。未易入侍。此可惜矣云云。正臣对曰。吾辈以秩卑讲官。虽不敢率尔陈戒。若因文起义而进戒。则恐无不可耶。说书曰。诺。如是酬酢之后。说书脱直。而吾则仍久在直。遂于二月三十日昼讲时。入侍书筵。因大学衍义第九卷诚意正心篇所引谷风章夫妇离绝国俗伤败之语。推演其义。缕缕陈戒。伊后司书说书相继陈戒之言。与正臣之言。互相表里。故两僚讲语并录于斯。庸识玆事之颠末矣。越数月李说书士珍。访余而言曰。日间因医官闻之。则吾辈陈戒之后。 春宫即辍外寝。入处嫔殿。此固数年以来所未有也。近又自上下教于内局。 春宫及嫔宫两殿所进求嗣方药物。连次剂进云。此实 宗社之庆云尔。○三月初一日召对时。宋鉴第六卷自孔彦舟穫钟相。止亦不敢复渡江矣。正臣奏曰。兀朮即金之主将。则兀朮之死生。实关金之存亡矣。韩世忠设伏于龙王庙。可谓料贼如神。而兀朮既危而复全。能脱于弥天之网。天
勉戒 春宫。俾令琴瑟合和。则岂非 宗社之福也。 上曰。予亦已屡度戒责。而不从予言。可闷。第当更为勉戒耳。领相兼世子师。故亦欲于入侍书筵时。勉戒 世子矣。意外被论于司谏尹世绥。方在引入。未易入侍。此可惜矣云云。正臣对曰。吾辈以秩卑讲官。虽不敢率尔陈戒。若因文起义而进戒。则恐无不可耶。说书曰。诺。如是酬酢之后。说书脱直。而吾则仍久在直。遂于二月三十日昼讲时。入侍书筵。因大学衍义第九卷诚意正心篇所引谷风章夫妇离绝国俗伤败之语。推演其义。缕缕陈戒。伊后司书说书相继陈戒之言。与正臣之言。互相表里。故两僚讲语并录于斯。庸识玆事之颠末矣。越数月李说书士珍。访余而言曰。日间因医官闻之。则吾辈陈戒之后。 春宫即辍外寝。入处嫔殿。此固数年以来所未有也。近又自上下教于内局。 春宫及嫔宫两殿所进求嗣方药物。连次剂进云。此实 宗社之庆云尔。○三月初一日召对时。宋鉴第六卷自孔彦舟穫钟相。止亦不敢复渡江矣。正臣奏曰。兀朮即金之主将。则兀朮之死生。实关金之存亡矣。韩世忠设伏于龙王庙。可谓料贼如神。而兀朮既危而复全。能脱于弥天之网。天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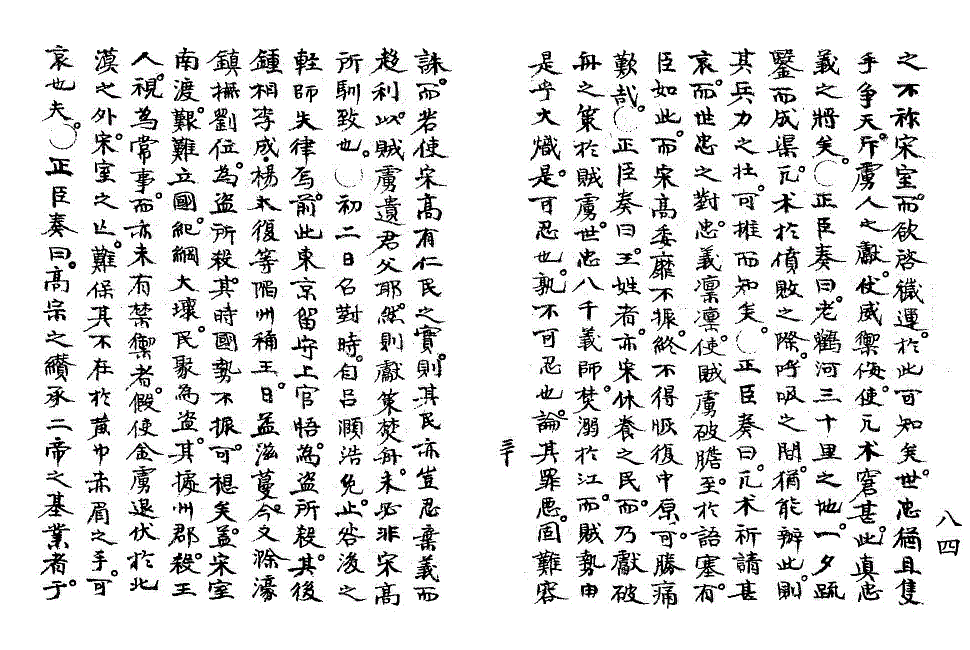 之不祚宋室。而欲启秽运。于此可知矣。世忠犹且只手争天。斥虏人之献。仗威御侮。使兀朮窘甚。此真忠义之将矣。○正臣奏曰。老鹳河三十里之地。一夕疏凿而成渠。兀朮于偾败之际。呼吸之间。犹能办此。则其兵力之壮。可推而知矣。○正臣奏曰。兀朮祈请甚哀。而世忠之对。忠义凛凛。使贼虏破胆。至于语塞。有臣如此。而宋高委靡不振。终不得恢复中原。可胜痛叹哉。○正臣奏曰。王姓者。亦宋休养之民。而乃献破舟之策于贼虏。世忠八千义师。焚溺于江。而贼势由是乎大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其罪恶。固难容诛。而若使宋高有仁民之实。则其民亦岂忍弃义而趍利。以贼虏遗君父耶。然则献策焚舟。未必非宋高所驯致也。○初二日召对时。自吕颐浩免。止咎浚之轻师失律焉。前此东京留守上官悟。为盗所杀。其后钟相李成,杨太复等陷州称王。日益滋蔓。今又滁濠镇抚刘位。为盗所杀。其时国势不振。可想矣。盖宋室南渡。艰难立国。纪纲大坏。民聚为盗。其据州郡。杀王人。视为常事。而亦未有禁御者。假使金虏退伏于北漠之外。宋室之亡。难保其不在于黄巾赤眉之手。可哀也夫。○正臣奏曰。高宗之缵承二帝之基业者。于
之不祚宋室。而欲启秽运。于此可知矣。世忠犹且只手争天。斥虏人之献。仗威御侮。使兀朮窘甚。此真忠义之将矣。○正臣奏曰。老鹳河三十里之地。一夕疏凿而成渠。兀朮于偾败之际。呼吸之间。犹能办此。则其兵力之壮。可推而知矣。○正臣奏曰。兀朮祈请甚哀。而世忠之对。忠义凛凛。使贼虏破胆。至于语塞。有臣如此。而宋高委靡不振。终不得恢复中原。可胜痛叹哉。○正臣奏曰。王姓者。亦宋休养之民。而乃献破舟之策于贼虏。世忠八千义师。焚溺于江。而贼势由是乎大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其罪恶。固难容诛。而若使宋高有仁民之实。则其民亦岂忍弃义而趍利。以贼虏遗君父耶。然则献策焚舟。未必非宋高所驯致也。○初二日召对时。自吕颐浩免。止咎浚之轻师失律焉。前此东京留守上官悟。为盗所杀。其后钟相李成,杨太复等陷州称王。日益滋蔓。今又滁濠镇抚刘位。为盗所杀。其时国势不振。可想矣。盖宋室南渡。艰难立国。纪纲大坏。民聚为盗。其据州郡。杀王人。视为常事。而亦未有禁御者。假使金虏退伏于北漠之外。宋室之亡。难保其不在于黄巾赤眉之手。可哀也夫。○正臣奏曰。高宗之缵承二帝之基业者。于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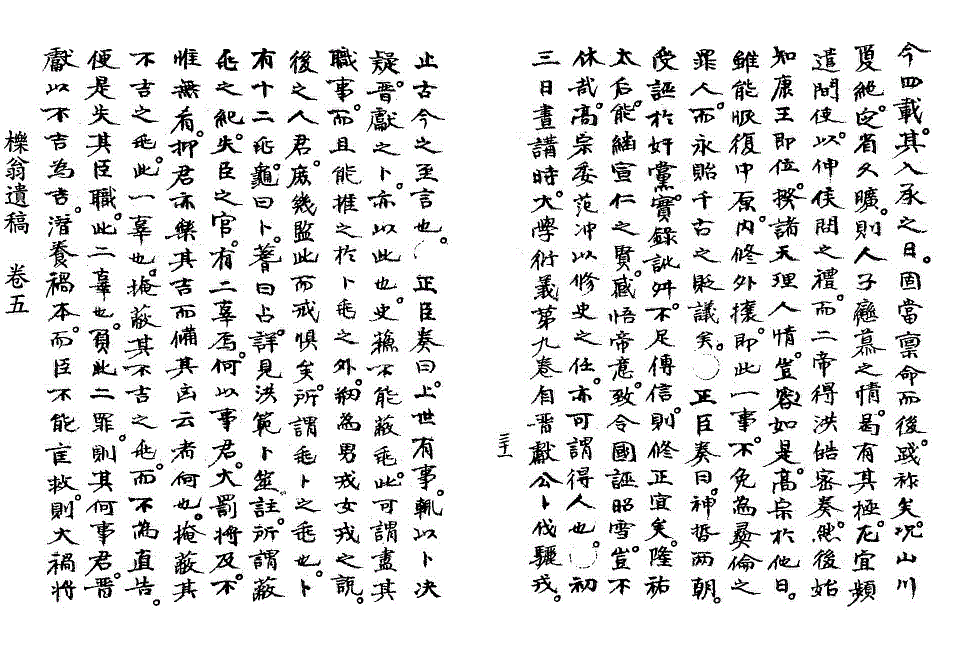 今四载。其入承之日。固当禀命而后。践祚矣。况山川夐绝。定省久旷。则人子恋慕之情。曷有其极。尤宜频遣间使。以伸候问之礼。而二帝得洪皓密奏。然后始知康王即位。揆诸天理人情。岂容如是。高宗于他日。虽能恢复中原。内修外攘。即此一事。不免为彝伦之罪人。而永贻千古之贬议矣。○正臣奏曰。神哲两朝。受诬于奸党。实录讹舛。不足传信。则修正宜矣。隆祐太后。能继宣仁之贤。感悟帝意。致令国诬昭雪。岂不休哉。高宗委范冲以修史之任。亦可谓得人也。○初三日昼讲时。大学衍义第九卷自晋献公卜伐骊戎。止古今之至言也。○正臣奏曰。上世有事。辄以卜决疑。晋献之卜。亦以此也。史苏不能蔽兆。此可谓尽其职事。而且能推之于卜兆之外。刱为男戎女戎之说。后之人君。庶几监此而戒惧矣。所谓兆卜之兆也。卜有十二兆。龟曰卜。蓍曰占。详见洪范卜筮注。所谓蔽兆之纪。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罚将及。不惟无肴。抑君亦乐其吉而备其凶云者何也。掩蔽其不吉之兆。此一辜也。掩蔽其不吉之兆。而不为直告。便是失其臣职。此二辜也。负此二罪。则其何事君。晋献以不吉为吉。潜养祸本。而臣不能匡救。则大祸将
今四载。其入承之日。固当禀命而后。践祚矣。况山川夐绝。定省久旷。则人子恋慕之情。曷有其极。尤宜频遣间使。以伸候问之礼。而二帝得洪皓密奏。然后始知康王即位。揆诸天理人情。岂容如是。高宗于他日。虽能恢复中原。内修外攘。即此一事。不免为彝伦之罪人。而永贻千古之贬议矣。○正臣奏曰。神哲两朝。受诬于奸党。实录讹舛。不足传信。则修正宜矣。隆祐太后。能继宣仁之贤。感悟帝意。致令国诬昭雪。岂不休哉。高宗委范冲以修史之任。亦可谓得人也。○初三日昼讲时。大学衍义第九卷自晋献公卜伐骊戎。止古今之至言也。○正臣奏曰。上世有事。辄以卜决疑。晋献之卜。亦以此也。史苏不能蔽兆。此可谓尽其职事。而且能推之于卜兆之外。刱为男戎女戎之说。后之人君。庶几监此而戒惧矣。所谓兆卜之兆也。卜有十二兆。龟曰卜。蓍曰占。详见洪范卜筮注。所谓蔽兆之纪。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罚将及。不惟无肴。抑君亦乐其吉而备其凶云者何也。掩蔽其不吉之兆。此一辜也。掩蔽其不吉之兆。而不为直告。便是失其臣职。此二辜也。负此二罪。则其何事君。晋献以不吉为吉。潜养祸本。而臣不能匡救。则大祸将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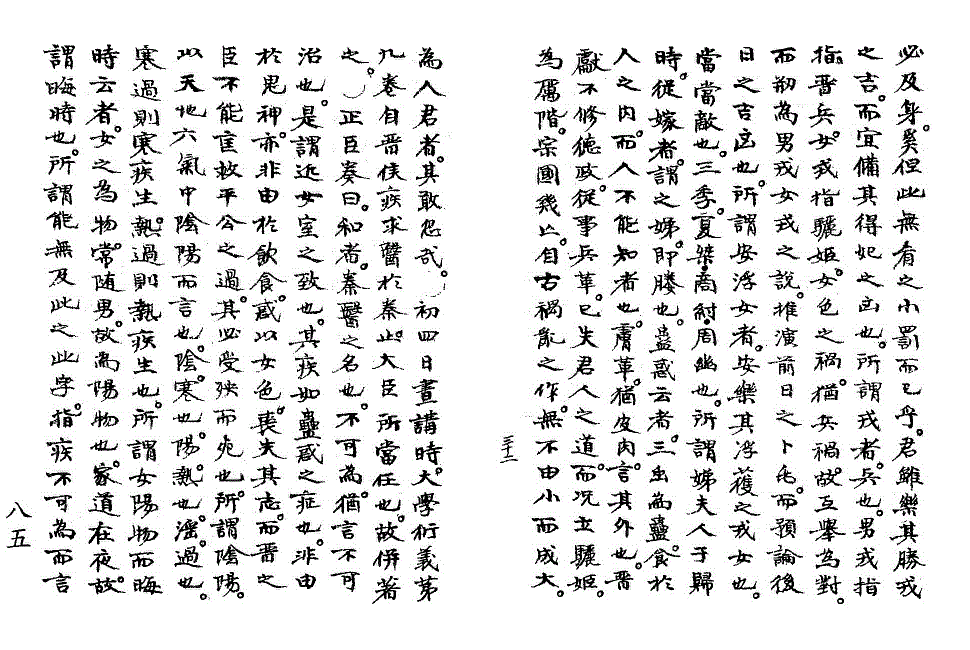 必及身。奚但此无肴之小罚而已乎。君虽乐其胜戎之吉。而宜备其得妃之凶也。所谓戎者。兵也。男戎指指(指衍字)晋兵。女戎指骊姬。女色之祸。犹兵祸。故互举为对。而刱为男戎女戎之说。推演前日之卜兆。而预论后日之吉凶也。所谓安浮女者。安乐其浮获之戎女也。当当敌也。三季。夏桀,商纣,周幽也。所谓娣夫人于归时。从嫁者。谓之娣。即媵也。蛊惑云者。三虫为蛊。食于人之内。而人不能知者也。肤革。犹皮肉。言其外也。晋献不修德政。从事兵革。已失君人之道。而况立骊姬。为厉阶。宗国几亡。自古祸乱之作。无不由小而成大。为人君者。其敢忽哉。○初四日昼讲时。大学衍义第九卷自晋侯疾求医于秦。止大臣所当任也。故并著之。○正臣奏曰。和者。秦医之名也。不可为。犹言不可治也。是谓近女室之致也。其疾如蛊惑之症也。非由于鬼神。亦非由于饮食。惑以女色。丧失其志。而晋之臣不能匡救平公之过。其必受殃而死也。所谓阴阳。以天地六气中阴阳而言也。阴。寒也。阳。热也。淫。过也。寒过则寒疾生。热过则热疾生也。所谓女阳物而晦时云者。女之为物。常随男。故为阳物也。家道在夜。故谓晦时也。所谓能无及此之此字。指疾不可为而言
必及身。奚但此无肴之小罚而已乎。君虽乐其胜戎之吉。而宜备其得妃之凶也。所谓戎者。兵也。男戎指指(指衍字)晋兵。女戎指骊姬。女色之祸。犹兵祸。故互举为对。而刱为男戎女戎之说。推演前日之卜兆。而预论后日之吉凶也。所谓安浮女者。安乐其浮获之戎女也。当当敌也。三季。夏桀,商纣,周幽也。所谓娣夫人于归时。从嫁者。谓之娣。即媵也。蛊惑云者。三虫为蛊。食于人之内。而人不能知者也。肤革。犹皮肉。言其外也。晋献不修德政。从事兵革。已失君人之道。而况立骊姬。为厉阶。宗国几亡。自古祸乱之作。无不由小而成大。为人君者。其敢忽哉。○初四日昼讲时。大学衍义第九卷自晋侯疾求医于秦。止大臣所当任也。故并著之。○正臣奏曰。和者。秦医之名也。不可为。犹言不可治也。是谓近女室之致也。其疾如蛊惑之症也。非由于鬼神。亦非由于饮食。惑以女色。丧失其志。而晋之臣不能匡救平公之过。其必受殃而死也。所谓阴阳。以天地六气中阴阳而言也。阴。寒也。阳。热也。淫。过也。寒过则寒疾生。热过则热疾生也。所谓女阳物而晦时云者。女之为物。常随男。故为阳物也。家道在夜。故谓晦时也。所谓能无及此之此字。指疾不可为而言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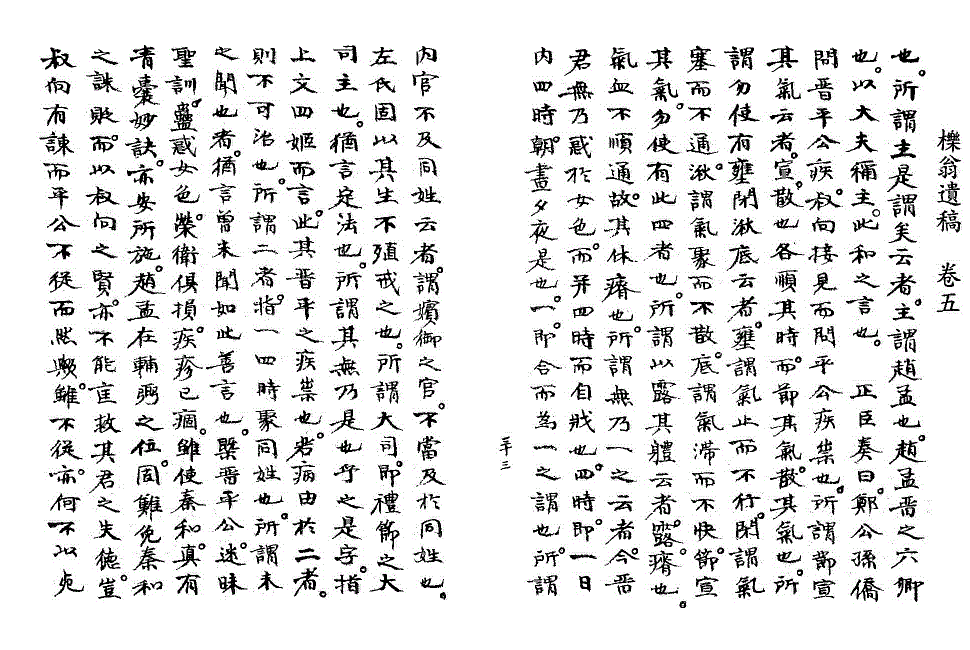 也。所谓主是谓矣云者。主谓赵孟也。赵孟晋之六卿也。以大夫称主。此和之言也。 正臣奏曰。郑公孙侨问晋平公疾。叔向接见而问平公疾祟也。所谓节宣其气云者。宣。散也各顺其时。而节其气。散其气也。所谓勿使有壅闭湫底云者。壅谓气止而不行。闭谓气塞而不通。湫谓气聚而不散。底谓气滞而不快。节宣其气。勿使有此四者也。所谓以露其体云者。露。瘠也。气血不顺通。故其休瘠也。所谓无乃一之云者。今晋君无乃惑于女色。而并四时而自戕也。四时。即一日内四时。朝昼夕夜是也。一。即合而为一之谓也。所谓内官不及同姓云者。谓嫔御之官。不当及于同姓也。左氏固以其生不殖戒之也。所谓大司。即礼节之大司主也。犹言定法也。所谓其无乃是也乎之是字。指上文四姬而言。此其晋平之疾祟也。若病由于二者。则不可治也。所谓二者。指一四时聚同姓也。所谓未之闻也者。犹言曾未闻如此善言也。槩晋平公。迷昧圣训。蛊惑女色。荣卫俱损。疾疹已痼。虽使秦和。真有青囊妙诀。亦安所施。赵孟在辅弼之位。固难免秦和之诛贬。而以叔向之贤。亦不能匡救其君之失德。岂叔向有谏而平公不从而然欤。虽不从。亦何不以死
也。所谓主是谓矣云者。主谓赵孟也。赵孟晋之六卿也。以大夫称主。此和之言也。 正臣奏曰。郑公孙侨问晋平公疾。叔向接见而问平公疾祟也。所谓节宣其气云者。宣。散也各顺其时。而节其气。散其气也。所谓勿使有壅闭湫底云者。壅谓气止而不行。闭谓气塞而不通。湫谓气聚而不散。底谓气滞而不快。节宣其气。勿使有此四者也。所谓以露其体云者。露。瘠也。气血不顺通。故其休瘠也。所谓无乃一之云者。今晋君无乃惑于女色。而并四时而自戕也。四时。即一日内四时。朝昼夕夜是也。一。即合而为一之谓也。所谓内官不及同姓云者。谓嫔御之官。不当及于同姓也。左氏固以其生不殖戒之也。所谓大司。即礼节之大司主也。犹言定法也。所谓其无乃是也乎之是字。指上文四姬而言。此其晋平之疾祟也。若病由于二者。则不可治也。所谓二者。指一四时聚同姓也。所谓未之闻也者。犹言曾未闻如此善言也。槩晋平公。迷昧圣训。蛊惑女色。荣卫俱损。疾疹已痼。虽使秦和。真有青囊妙诀。亦安所施。赵孟在辅弼之位。固难免秦和之诛贬。而以叔向之贤。亦不能匡救其君之失德。岂叔向有谏而平公不从而然欤。虽不从。亦何不以死栎翁遗稿卷之五 第 86L 页
 力争欤。后之为人君为人臣者。宜监于此。各勉其所当为者也。○王世子问曰。晋侯疾求医章。公曰。女不可近乎云者。何谓也。正臣窃伏思之。 春宫发问之微意。似不在于本章之义。前月三十日昼讲。就谷风章进讲时。正臣以夫妇和合之义。缕缕陈戒。则今此女不可近乎之言。与前陈戒之言。有若径庭。故俯询之意。或者因此而发矣。正臣遂起拜而对曰。男女相近。固有之理也。秦和本责其近女室过度。而非以相近为咎也。晋平沉迷女色。失其良智。谬疑秦和以女室谓不可近。而乃有此问。可谓惑之甚矣。周文王与太姒。友以琴瑟。乐以钟鼓。则不特相近而已。而乃能寿考无疆。德化大行。伏愿 邸下。其监于玆。以周文王为法。而以晋平公为戒焉。
力争欤。后之为人君为人臣者。宜监于此。各勉其所当为者也。○王世子问曰。晋侯疾求医章。公曰。女不可近乎云者。何谓也。正臣窃伏思之。 春宫发问之微意。似不在于本章之义。前月三十日昼讲。就谷风章进讲时。正臣以夫妇和合之义。缕缕陈戒。则今此女不可近乎之言。与前陈戒之言。有若径庭。故俯询之意。或者因此而发矣。正臣遂起拜而对曰。男女相近。固有之理也。秦和本责其近女室过度。而非以相近为咎也。晋平沉迷女色。失其良智。谬疑秦和以女室谓不可近。而乃有此问。可谓惑之甚矣。周文王与太姒。友以琴瑟。乐以钟鼓。则不特相近而已。而乃能寿考无疆。德化大行。伏愿 邸下。其监于玆。以周文王为法。而以晋平公为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