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x 页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杂著
杂著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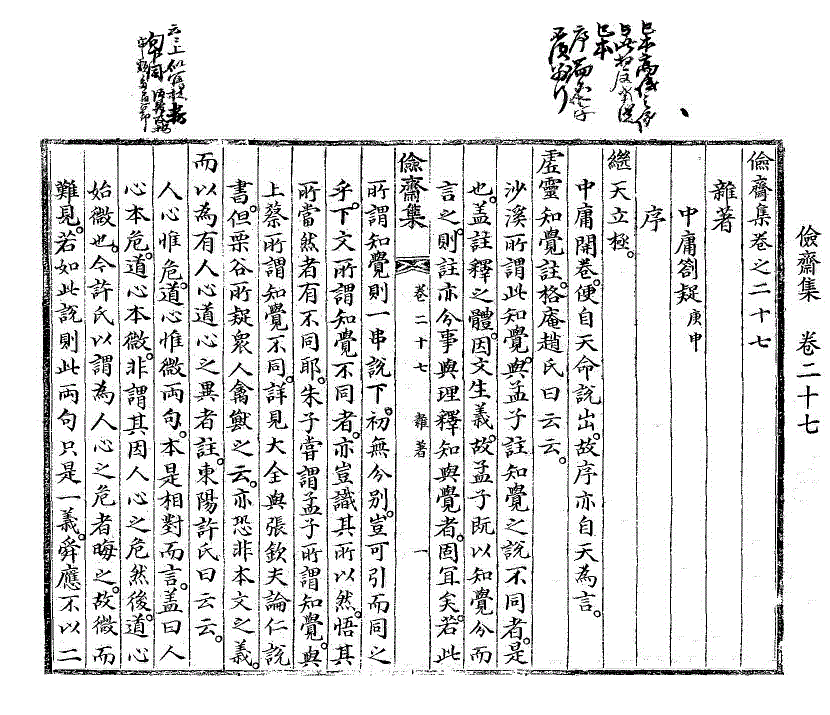 中庸劄疑(庚申)
中庸劄疑(庚申)序
继天立极。
中庸开卷。便自天命说出。故序亦自天为言。
虚灵知觉注。格庵赵氏曰云云。
沙溪所谓此知觉。与孟子注知觉之说不同者。是也。盖注释之体。因文生义。故孟子既以知觉分而言之。则注亦分事与理释知与觉者。固宜矣。若此所谓知觉则一串说下。初无分别。岂可引而同之乎。下文所谓知觉不同者。亦岂识其所以然。悟其所当然者有不同耶。朱子尝谓孟子所谓知觉。与上蔡所谓知觉不同。详见大全与张钦夫论仁说书。但栗谷所疑众人禽兽之云。亦恐非本文之义。
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注。东阳许氏曰云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两句。本是相对而言。盖曰人心本危。道心本微。非谓其因人心之危然后。道心始微也。今许氏以谓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难见。若如此说则此两句只是一义。舜应不以二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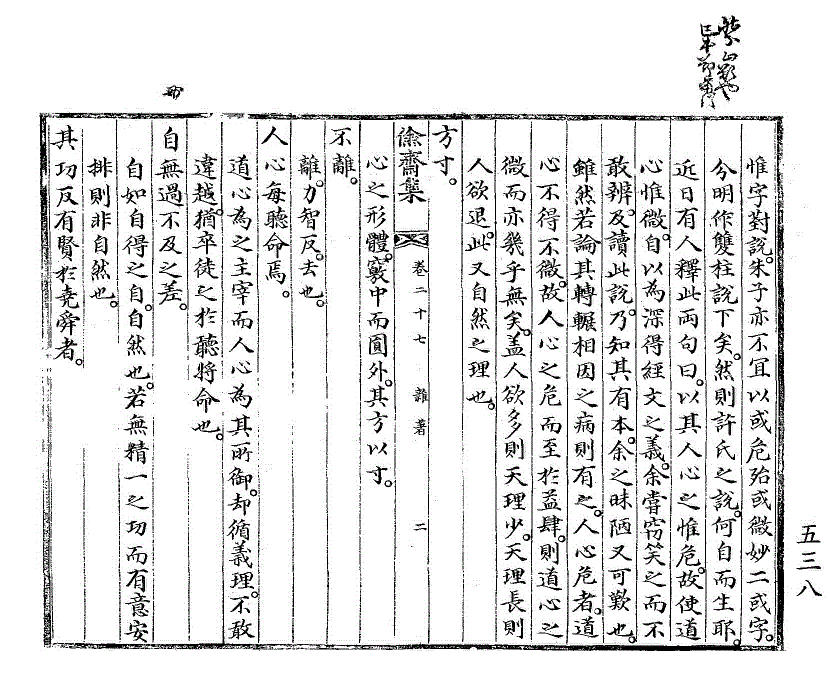 惟字对说。朱子亦不宜以或危殆或微妙二或字。分明作双柱说下矣。然则许氏之说。何自而生耶。近日有人释此两句曰。以其人心之惟危。故使道心惟微。自以为深得经文之义。余尝窃笑之而不敢辨。及读此说。乃知其有本。余之昧陋又可叹也。虽然若论其转辗相因之病则有之。人心危者。道心不得不微。故人心之危而至于益肆。则道心之微而亦几乎无矣。盖人欲多则天理少。天理长则人欲退。此又自然之理也。
惟字对说。朱子亦不宜以或危殆或微妙二或字。分明作双柱说下矣。然则许氏之说。何自而生耶。近日有人释此两句曰。以其人心之惟危。故使道心惟微。自以为深得经文之义。余尝窃笑之而不敢辨。及读此说。乃知其有本。余之昧陋又可叹也。虽然若论其转辗相因之病则有之。人心危者。道心不得不微。故人心之危而至于益肆。则道心之微而亦几乎无矣。盖人欲多则天理少。天理长则人欲退。此又自然之理也。方寸。
心之形体。窍中而圆外。其方以寸。
不离。
离。力智反。去也。
人心每听命焉。
道心为之主宰而人心为其所御。却循义理。不敢违越。犹卒徒之于听将命也。
自无过不及之差。
自如自得之自。自然也。若无精一之功而有意安排则非自然也。
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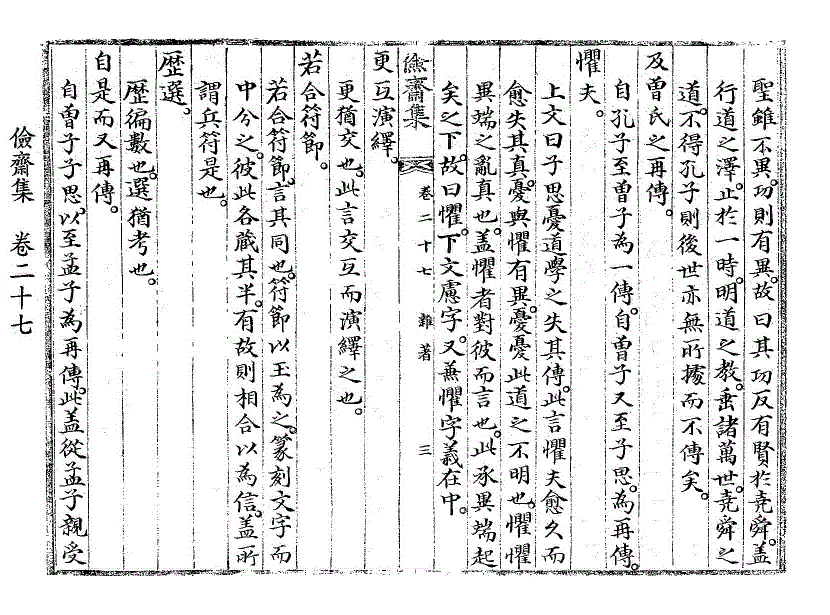 圣虽不异。功则有异。故曰其功反有贤于尧舜。盖行道之泽。止于一时。明道之教。垂诸万世。尧舜之道。不得孔子则后世亦无所据而不传矣。
圣虽不异。功则有异。故曰其功反有贤于尧舜。盖行道之泽。止于一时。明道之教。垂诸万世。尧舜之道。不得孔子则后世亦无所据而不传矣。及曾氏之再传。
自孔子至曾子为一传。自曾子又至子思。为再传。
惧夫。
上文曰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此言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忧与惧有异。忧忧此道之不明也。惧惧异端之乱真也。盖惧者对彼而言也。此承异端起矣之下。故曰惧。下文虑字。又兼惧字义在中。
更互演绎。
更犹交也。此言交互而演绎之也。
若合符节。
若合符节。言其同也。符节以玉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则相合以为信。盖所谓兵符是也。
历选。
历遍数也。选犹考也。
自是而又再传。
自曾子子思。以至孟子为再传。此盖从孟子亲受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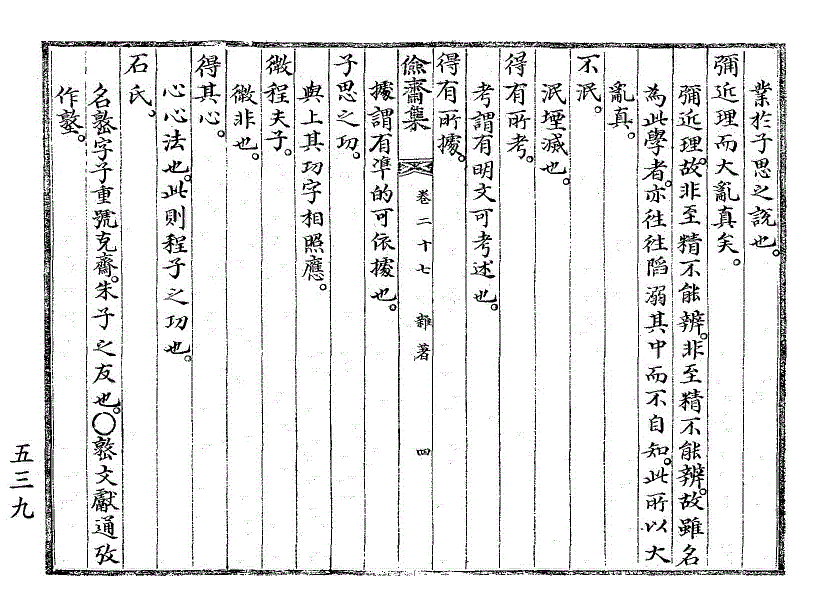 业于子思之说也。
业于子思之说也。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弥近理。故非至精不能辨。非至精不能辨。故虽名为此学者。亦往往陷溺其中而不自知。此所以大乱真。
不泯。
泯堙灭也。
得有所考。
考谓有明文可考述也。
得有所据。
据谓有准的可依据也。
子思之功。
与上其功字相照应。
微程夫子。
微非也。
得其心。
心心法也。此则程子之功也。
石氏。
名𡼖字子重号克斋。朱子之友也。○𡼖文献通考作墩。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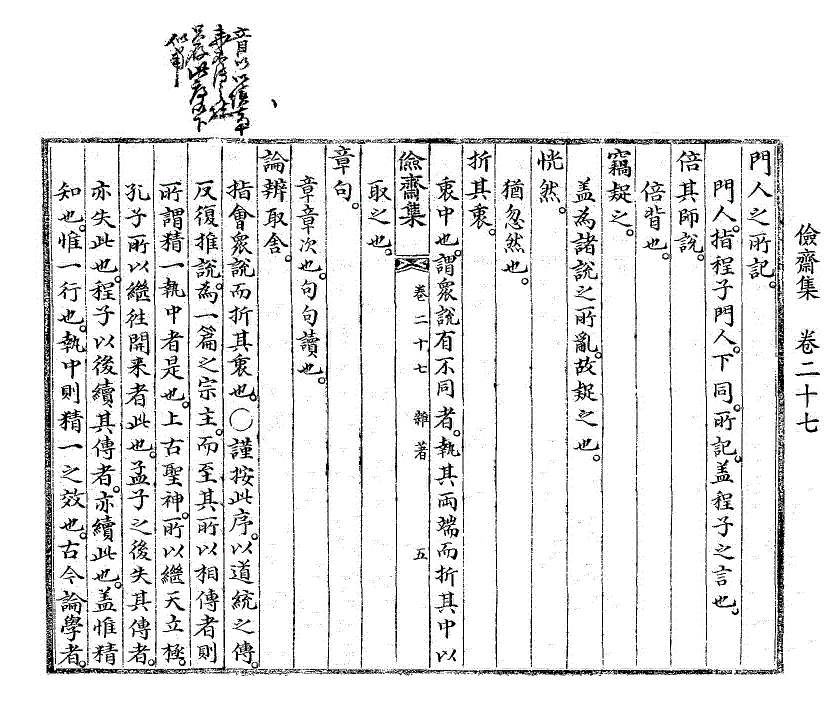 门人之所记。
门人之所记。门人。指程子门人。下同。所记。盖程子之言也。
倍其师说。
倍背也。
窃疑之。
盖为诸说之所乱。故疑之也。
恍然。
犹忽然也。
折其衷。
衷中也。谓众说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折其中以取之也。
章句。
章章次也。句句读也。
论辨取舍。
指会众说而折其衷也。○谨按此序。以道统之传。反复推说。为一篇之宗主。而至其所以相传者则所谓精一执中者是也。上古圣神。所以继天立极。孔子所以继往开来者此也。孟子之后失其传者。亦失此也。程子以后续其传者。亦续此也。盖惟精知也。惟一行也。执中则精一之效也。古今论学者。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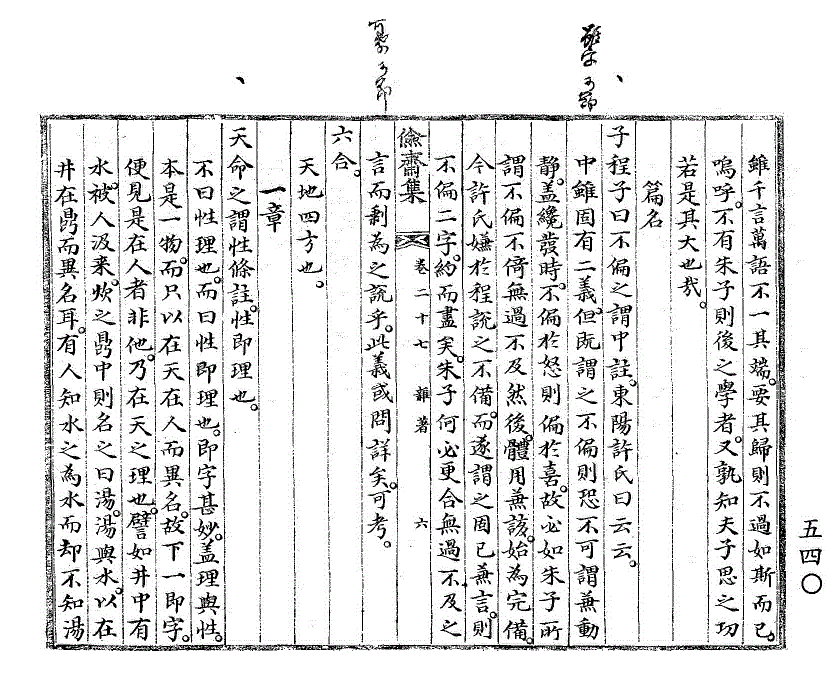 虽千言万语不一其端。要其归则不过如斯而已。呜呼。不有朱子则后之学者。又孰知夫子思之功若是其大也哉。
虽千言万语不一其端。要其归则不过如斯而已。呜呼。不有朱子则后之学者。又孰知夫子思之功若是其大也哉。篇名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注。东阳许氏曰云云。
中虽固有二义。但既谓之不偏则恐不可谓兼动静。盖才发时。不偏于怒则偏于喜。故必如朱子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然后。体用兼该。始为完备。今许氏嫌于程说之不备。而遂谓之固已兼言。则不偏二字。约而尽矣。朱子何必更合无过不及之言而剩为之说乎。此义或问详矣。可考。
六合。
天地四方也。
一章
天命之谓性条注。性即理也。
不曰性理也。而曰性即理也。即字甚妙。盖理与性。本是一物。而只以在天在人而异名。故下一即字。便见是在人者非他。乃在天之理也。譬如井中有水。被人汲来。炊之鼎中则名之曰汤。汤与水。以在井在鼎而异名耳。有人知水之为水而却不知汤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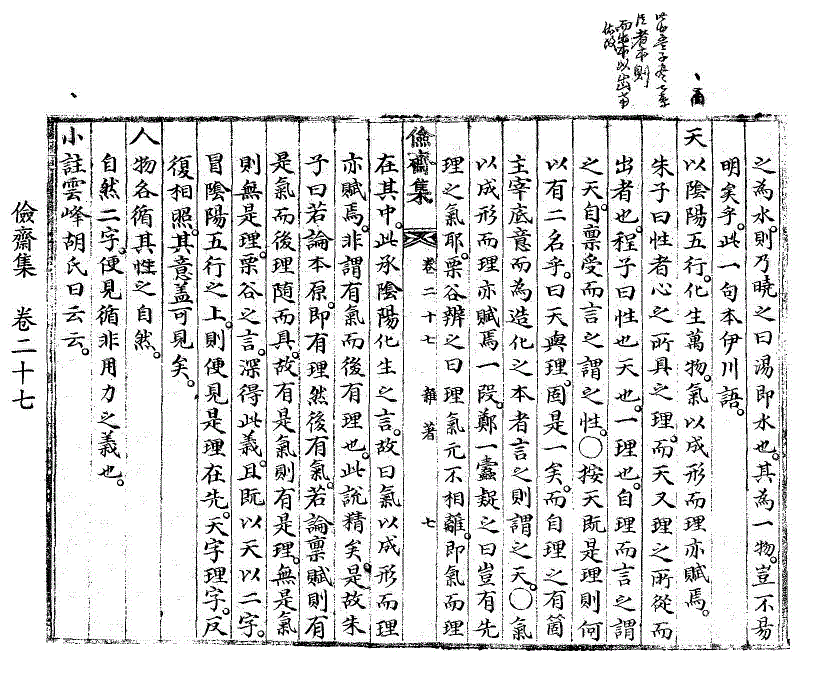 之为水。则乃晓之曰汤即水也。其为一物。岂不易明矣乎。此一句本伊川语。
之为水。则乃晓之曰汤即水也。其为一物。岂不易明矣乎。此一句本伊川语。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
朱子曰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而出者也。程子曰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而言之谓之性。○按天既是理则何以有二名乎。曰天与理。固是一矣。而自理之有个主宰底意而为造化之本者言之则谓之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一段。郑一蠹疑之曰岂有先理之气耶。栗谷辨之曰理气元不相离。即气而理在其中。此承阴阳化生之言。故曰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非谓有气而后有理也。此说精矣。是故朱子曰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而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栗谷之言。深得此义。且既以天以二字。冒阴阳五行之上。则便见是理在先。天字理字。反复相照。其意盖可见矣。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自然二字。便见循非用力之义也。
小注云峰胡氏曰云云。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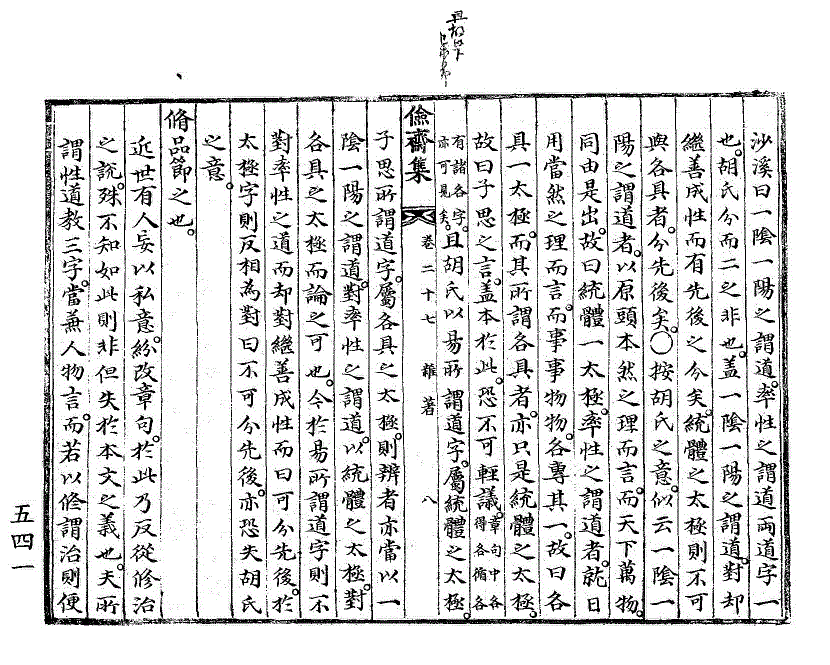 沙溪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率性之谓道两道字一也。胡氏分而二之非也。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却继善成性而有先后之分矣。统体之太极则不可与各具者。分先后矣。○按胡氏之意。似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以原头本然之理而言。而天下万物。同由是出。故曰统体一太极。率性之谓道者。就日用当然之理而言。而事事物物。各专其一。故曰各具一太极。而其所谓各具者。亦只是统体之太极。故曰子思之言。盖本于此。恐不可轻议。(章句中各得各循各有诸各字。亦可见矣。)且胡氏以易所谓道字。属统体之太极。子思所谓道字。属各具之太极。则辨者亦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率性之谓道。以统体之太极。对各具之太极而论之可也。今于易所谓道字则不对率性之道而却对继善成性而曰可分先后。于太极字则反相为对曰不可分先后。亦恐失胡氏之意。
沙溪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率性之谓道两道字一也。胡氏分而二之非也。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却继善成性而有先后之分矣。统体之太极则不可与各具者。分先后矣。○按胡氏之意。似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以原头本然之理而言。而天下万物。同由是出。故曰统体一太极。率性之谓道者。就日用当然之理而言。而事事物物。各专其一。故曰各具一太极。而其所谓各具者。亦只是统体之太极。故曰子思之言。盖本于此。恐不可轻议。(章句中各得各循各有诸各字。亦可见矣。)且胡氏以易所谓道字。属统体之太极。子思所谓道字。属各具之太极。则辨者亦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率性之谓道。以统体之太极。对各具之太极而论之可也。今于易所谓道字则不对率性之道而却对继善成性而曰可分先后。于太极字则反相为对曰不可分先后。亦恐失胡氏之意。脩品节之也。
近世有人妄以私意。纷改章句。于此乃反从修治之说。殊不知如此则非但失于本文之义也。夫所谓性道教三字。当兼人物言。而若以修谓治则便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2H 页
 脱却物一边而可乎。其好异亦甚矣。○朱夫子承前启后。理明义精。积于中而发于外。故其于解释经旨。凡一字一义。无非衡尺之当。则如至圆不能加规。如至方不能加矩。盖集群贤之大成。而天下之理。于是乎无复馀蕴矣。后之学者。其能者固默而循之而已。其不能者。当反覆研究。思之思之。必以求合乎其说可也。不可以昏蔽之见。暂而有疑于其心则辄肆然立说。生怪出异。以自陷于无圣之罪。如此者譬如悖道梗化之民也。论以春秋之法则人人得而诛之者是也。呜呼可胜言哉。邪说害正。如陆氏佛氏老氏之说。其来虽旧。而幸而见正于程朱。故其祸不博。至于此一种求异好奇之论则有足以新一时之听而适厌常之情。故才高者易惑而卑者又不知所以辨。是以坏人心术于潜隐幽暗之中。而其祸至于猖狂恣睢。无所忌惮而后已焉。学者又不可以不戒。故余因论之。
脱却物一边而可乎。其好异亦甚矣。○朱夫子承前启后。理明义精。积于中而发于外。故其于解释经旨。凡一字一义。无非衡尺之当。则如至圆不能加规。如至方不能加矩。盖集群贤之大成。而天下之理。于是乎无复馀蕴矣。后之学者。其能者固默而循之而已。其不能者。当反覆研究。思之思之。必以求合乎其说可也。不可以昏蔽之见。暂而有疑于其心则辄肆然立说。生怪出异。以自陷于无圣之罪。如此者譬如悖道梗化之民也。论以春秋之法则人人得而诛之者是也。呜呼可胜言哉。邪说害正。如陆氏佛氏老氏之说。其来虽旧。而幸而见正于程朱。故其祸不博。至于此一种求异好奇之论则有足以新一时之听而适厌常之情。故才高者易惑而卑者又不知所以辨。是以坏人心术于潜隐幽暗之中。而其祸至于猖狂恣睢。无所忌惮而后已焉。学者又不可以不戒。故余因论之。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
上文兼人物言。此处专以人言。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条注。常存敬畏小注。敬谓戒慎。畏谓恐惧。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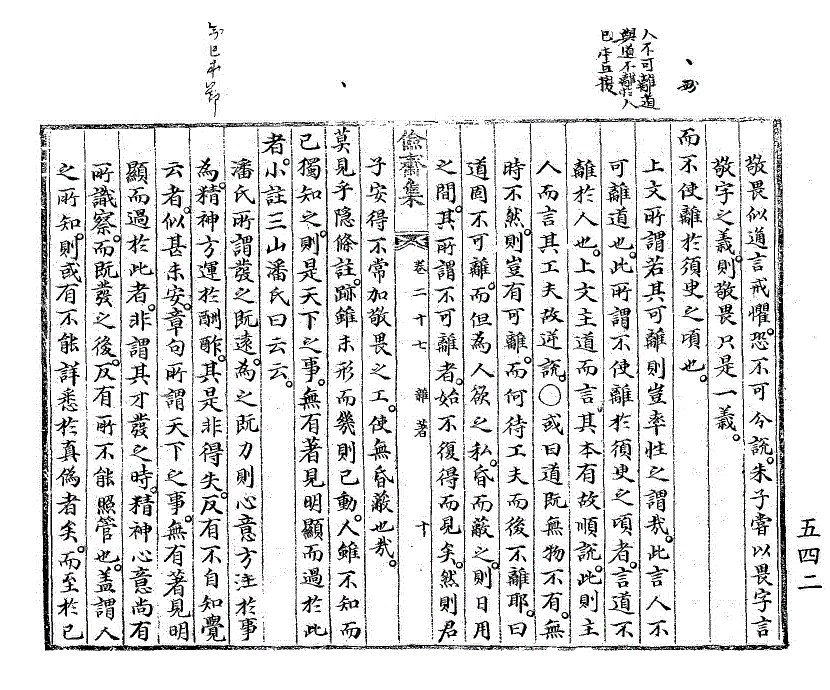 敬畏似通言戒惧。恐不可分说。朱子尝以畏字言敬字之义。则敬畏只是一义。
敬畏似通言戒惧。恐不可分说。朱子尝以畏字言敬字之义。则敬畏只是一义。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上文所谓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此言人不可离道也。此所谓不使离于须臾之顷者。言道不离于人也。上文主道而言其本有故顺说。此则主人而言其工夫故逆说。○或曰道既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则岂有可离。而何待工夫而后不离耶。曰道固不可离。而但为人欲之私。昏而蔽之。则日用之间。其所谓不可离者。始不复得而见矣。然则君子安得不常加敬畏之工。使无昏蔽也哉。
莫见乎隐条注。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小注三山潘氏曰云云。
潘氏所谓发之既远。为之既力则心意方注于事为。精神方运于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知觉云者。似甚未安。章句所谓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非谓其才发之时。精神心意尚有所识察。而既发之后。反有所不能照管也。盖谓人之所知。则或有不能详悉于真伪者矣。而至于己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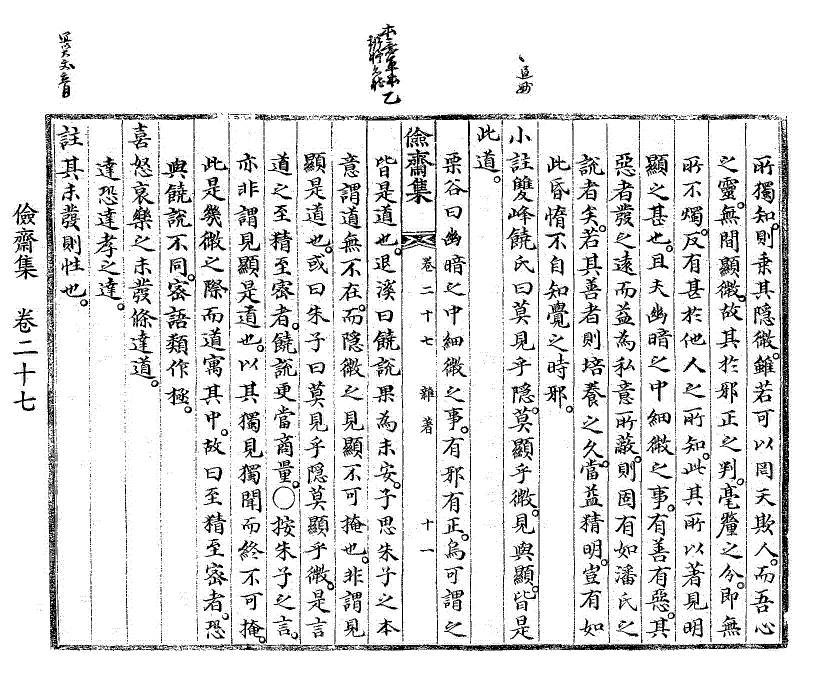 所独知。则乘其隐微。虽若可以罔天欺人。而吾心之灵。无间显微。故其于邪正之判。毫釐之分。即无所不烛。反有甚于他人之所知。此其所以著见明显之甚也。且夫幽暗之中细微之事。有善有恶。其恶者发之远而益为私意所蔽。则固有如潘氏之说者矣。若其善者则培养之久。当益精明。岂有如此昏惰不自知觉之时邪。
所独知。则乘其隐微。虽若可以罔天欺人。而吾心之灵。无间显微。故其于邪正之判。毫釐之分。即无所不烛。反有甚于他人之所知。此其所以著见明显之甚也。且夫幽暗之中细微之事。有善有恶。其恶者发之远而益为私意所蔽。则固有如潘氏之说者矣。若其善者则培养之久。当益精明。岂有如此昏惰不自知觉之时邪。小注双峰饶氏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见与显。皆是此道。
栗谷曰幽暗之中细微之事。有邪有正。乌可谓之皆是道也。退溪曰饶说果为未安。子思朱子之本意谓道无不在。而隐微之见显不可掩也。非谓见显是道也。或曰朱子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饶说更当商量。○按朱子之言。亦非谓见显是道也。以其独见独闻而终不可掩。此是几微之际而道寓其中。故曰至精至密者。恐与饶说不同。密语类作极。
喜怒哀乐之未发条达道。
达恐达孝之达。
注其未发则性也。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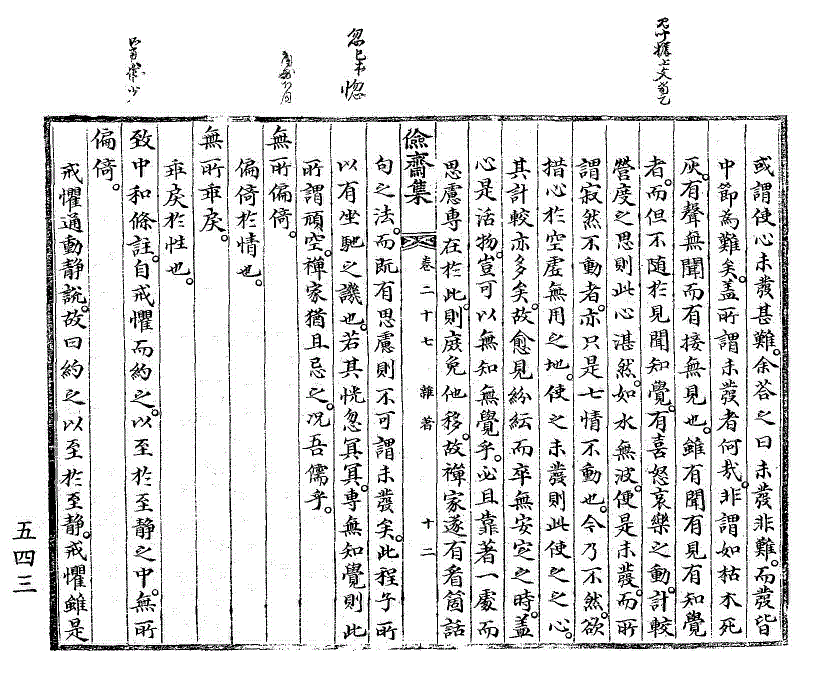 或谓使心未发甚难。余答之曰未发非难。而发皆中节为难矣。盖所谓未发者何哉。非谓如枯木死灰。有声无闻而有接无见也。虽有闻有见有知觉者。而但不随于见闻知觉。有喜怒哀乐之动。计较营度之思则此心湛然。如水无波。便是未发。而所谓寂然不动者。亦只是七情不动也。今乃不然。欲措心于空虚无用之地。使之未发则此使之之心。其计较亦多矣。故愈见纷纭而卒无安定之时。盖心是活物。岂可以无知无觉乎。必且靠著一处而思虑专在于此。则庶免他移。故禅家遂有看个话句之法。而既有思虑则不可谓未发矣。此程子所以有坐驰之讥也。若其恍忽冥冥。专无知觉则此所谓顽空。禅家犹且忌之。况吾儒乎。
或谓使心未发甚难。余答之曰未发非难。而发皆中节为难矣。盖所谓未发者何哉。非谓如枯木死灰。有声无闻而有接无见也。虽有闻有见有知觉者。而但不随于见闻知觉。有喜怒哀乐之动。计较营度之思则此心湛然。如水无波。便是未发。而所谓寂然不动者。亦只是七情不动也。今乃不然。欲措心于空虚无用之地。使之未发则此使之之心。其计较亦多矣。故愈见纷纭而卒无安定之时。盖心是活物。岂可以无知无觉乎。必且靠著一处而思虑专在于此。则庶免他移。故禅家遂有看个话句之法。而既有思虑则不可谓未发矣。此程子所以有坐驰之讥也。若其恍忽冥冥。专无知觉则此所谓顽空。禅家犹且忌之。况吾儒乎。无所偏倚。
偏倚于情也。
无所乖戾。
乖戾于性也。
致中和条注。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
戒惧通动静说。故曰约之以至于至静。戒惧虽是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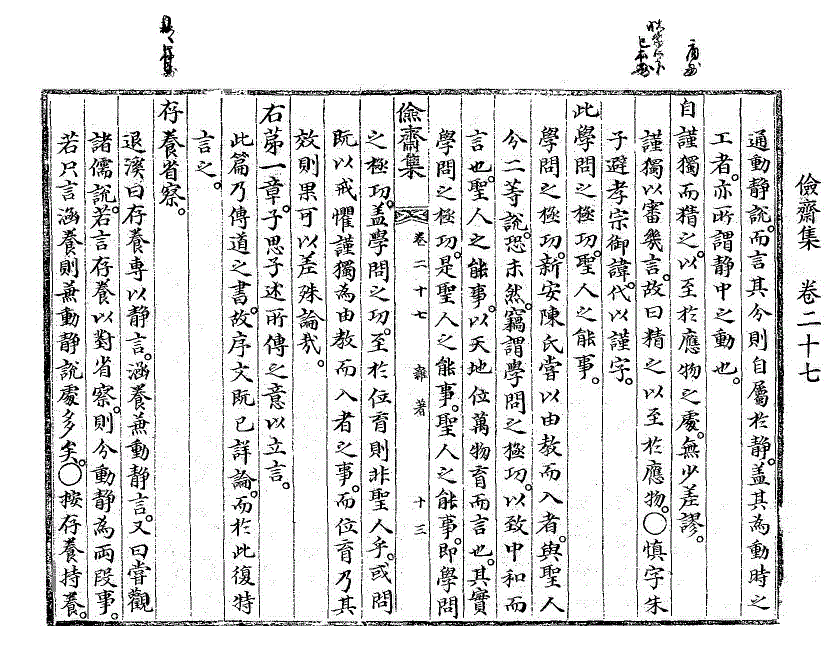 通动静说。而言其分则自属于静。盖其为动时之工者。亦所谓静中之动也。
通动静说。而言其分则自属于静。盖其为动时之工者。亦所谓静中之动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
谨独以审几言。故曰精之以至于应物。○慎字朱子避孝宗御讳。代以谨字。
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
学问之极功。新安陈氏尝以由教而入者。与圣人分二等说。恐未然。窃谓学问之极功。以致中和而言也。圣人之能事。以天地位万物育而言也。其实学问之极功。是圣人之能事。圣人之能事。即学问之极功。盖学问之功。至于位育则非圣人乎。或问既以戒惧谨独为由教而入者之事。而位育乃其效则果可以差殊论哉。
右第一章。子思子述所传之意以立言。
此篇乃传道之书。故序文既已详论。而于此复特言之。
存养省察。
退溪曰存养专以静言。涵养兼动静言。又曰尝观诸儒说。若言存养以对省察。则分动静为两段事。若只言涵养则兼动静说处多矣。○按存养持养。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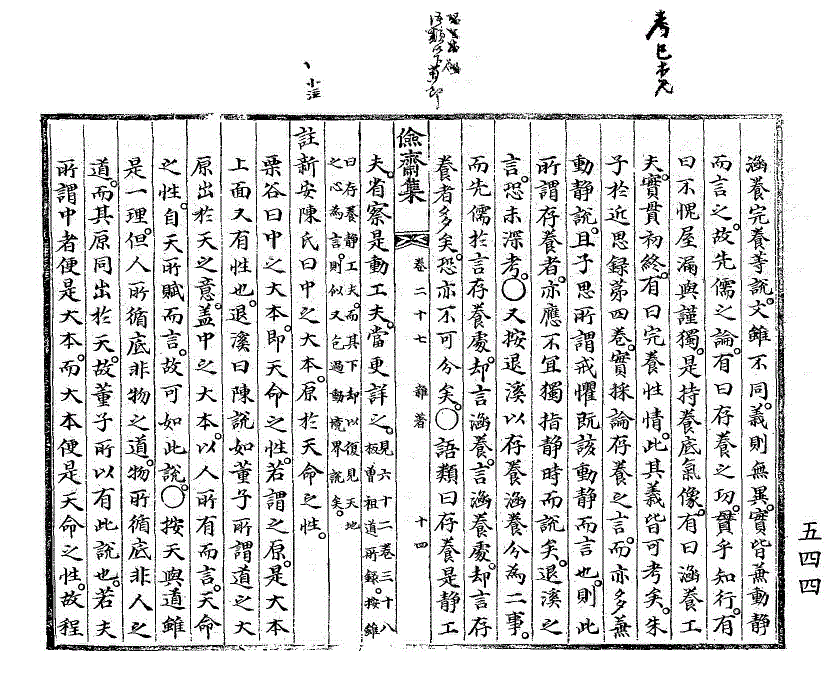 涵养完养等说。文虽不同。义则无异。实皆兼动静而言之。故先儒之论。有曰存养之功。贯乎知行。有曰不愧屋漏与谨独。是持养底气像。有曰涵养工夫。实贯初终。有曰完养性情。此其义皆可考矣。朱子于近思录第四卷。实采论存养之言。而亦多兼动静说。且子思所谓戒惧既该动静而言也。则此所谓存养者。亦应不宜独指静时而说矣。退溪之言。恐未深考。○又按退溪以存养涵养分为二事。而先儒于言存养处。却言涵养。言涵养处。却言存养者多矣。恐亦不可分矣。○语类曰存养是静工夫。省察是动工夫。当更详之。(见六十二卷三十八板曾祖道所录。按虽曰存养静工夫。而其下却以复见天地之心为言。则似又包过动境界说矣。)
涵养完养等说。文虽不同。义则无异。实皆兼动静而言之。故先儒之论。有曰存养之功。贯乎知行。有曰不愧屋漏与谨独。是持养底气像。有曰涵养工夫。实贯初终。有曰完养性情。此其义皆可考矣。朱子于近思录第四卷。实采论存养之言。而亦多兼动静说。且子思所谓戒惧既该动静而言也。则此所谓存养者。亦应不宜独指静时而说矣。退溪之言。恐未深考。○又按退溪以存养涵养分为二事。而先儒于言存养处。却言涵养。言涵养处。却言存养者多矣。恐亦不可分矣。○语类曰存养是静工夫。省察是动工夫。当更详之。(见六十二卷三十八板曾祖道所录。按虽曰存养静工夫。而其下却以复见天地之心为言。则似又包过动境界说矣。)注新安陈氏曰中之大本。原于天命之性。
栗谷曰中之大本。即天命之性。若谓之原。是大本上面又有性也。退溪曰陈说如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之意。盖中之大本。以人所有而言。天命之性。自天所赋而言。故可如此说。○按天与道虽是一理。但人所循底非物之道。物所循底非人之道。而其原同出于天。故董子所以有此说也。若夫所谓中者便是大本。而大本便是天命之性。故程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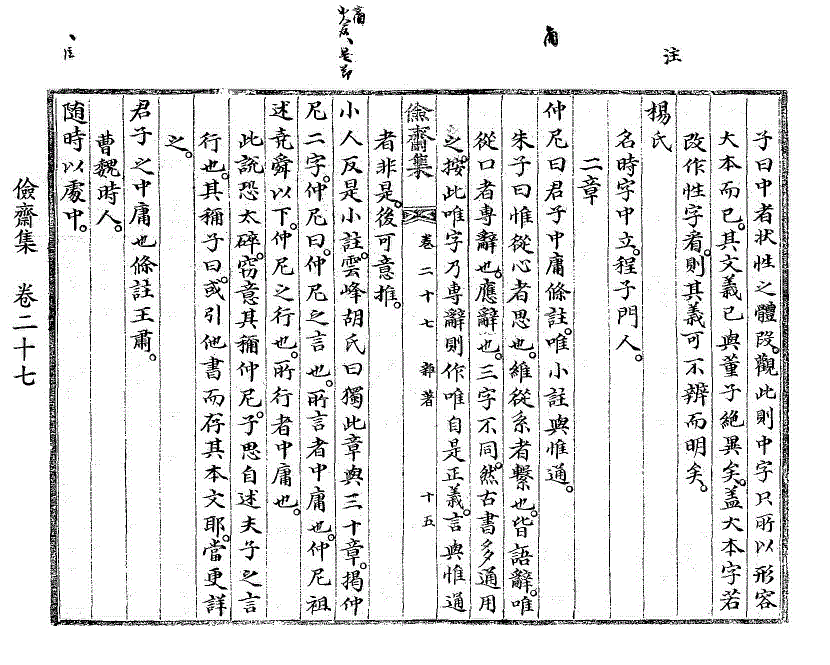 子曰中者状性之体段。观此则中字只所以形容大本而已。其文义已与董子绝异矣。盖大本字若改作性字看。则其义可不辨而明矣。
子曰中者状性之体段。观此则中字只所以形容大本而已。其文义已与董子绝异矣。盖大本字若改作性字看。则其义可不辨而明矣。杨氏
名时字中立。程子门人。
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条注。唯小注与惟通。
朱子曰惟从心者思也。维从系者系也。皆语辞。唯从口者专辞也。应辞也。三字不同。然古书多通用之。按此唯字乃专辞则作唯自是正义。言与惟通者非是。后可意推。
小人反是小注。云峰胡氏曰独此章与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中庸也。
此说恐太碎。窃意其称仲尼。子思自述夫子之言行也。其称子曰。或引他书而存其本文耶。当更详之。
君子之中庸也条注王肃。
曹魏时人。
随时以处中。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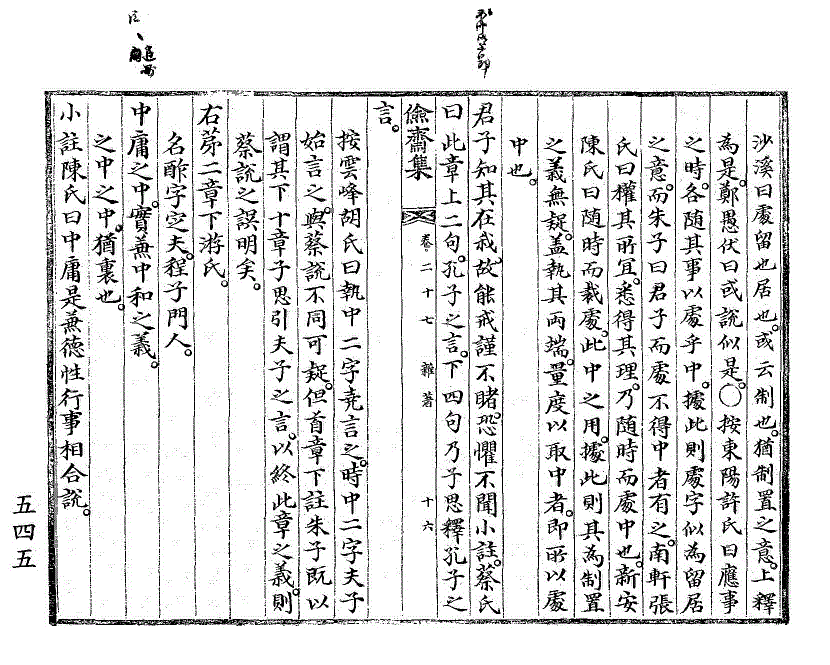 沙溪曰处留也居也。或云制也。犹制置之意。上释为是。郑愚伏曰或说似是。○按东阳许氏曰应事之时。各随其事以处乎中。据此则处字似为留居之意。而朱子曰君子而处不得中者有之。南轩张氏曰权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随时而处中也。新安陈氏曰随时而裁处。此中之用。据此则其为制置之义无疑。盖执其两端。量度以取中者。即所以处中也。
沙溪曰处留也居也。或云制也。犹制置之意。上释为是。郑愚伏曰或说似是。○按东阳许氏曰应事之时。各随其事以处乎中。据此则处字似为留居之意。而朱子曰君子而处不得中者有之。南轩张氏曰权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随时而处中也。新安陈氏曰随时而裁处。此中之用。据此则其为制置之义无疑。盖执其两端。量度以取中者。即所以处中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小注。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释孔子之言。
按云峰胡氏曰执中二字尧言之。时中二字夫子始言之。与蔡说不同可疑。但首章下注朱子既以谓其下十章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则蔡说之误明矣。
右第二章下游氏。
名酢字定夫。程子门人。
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之中之中。犹里也。
小注陈氏曰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说。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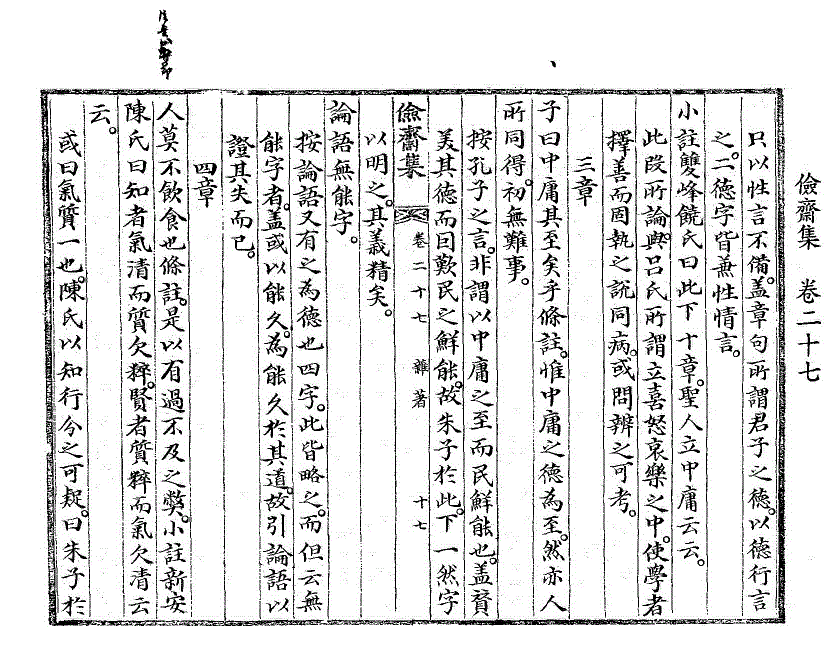 只以性言不备。盖章句所谓君子之德。以德行言之。二德字皆兼性情言。
只以性言不备。盖章句所谓君子之德。以德行言之。二德字皆兼性情言。小注双峰饶氏曰此下十章。圣人立中庸云云。
此段所论。与吕氏所谓立喜怒哀乐之中。使学者择善而固执之说同病。或问辨之可考。
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条注。惟中庸之德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
按孔子之言。非谓以中庸之至而民鲜能也。盖赞美其德而因叹民之鲜能。故朱子于此。下一然字以明之。其义精矣。
论语无能字。
按论语又有之为德也四字。此皆略之。而但云无能字者。盖或以能久。为能久于其道。故引论语以證其失而已。
四章
人莫不饮食也条注。是以有过不及之弊。小注新安陈氏曰知者气清而质欠粹。贤者质粹而气欠清云云。
或曰气质一也。陈氏以知行分之可疑。曰朱子于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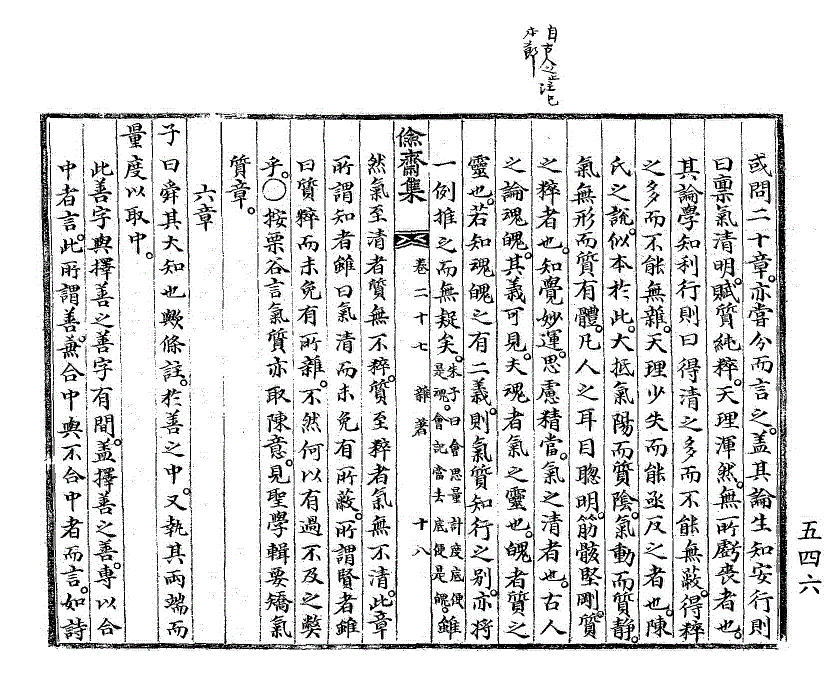 或问二十章。亦尝分而言之。盖其论生知安行则曰禀气清明。赋质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丧者也。其论学知利行则曰得清之多而不能无蔽。得粹之多而不能无杂。天理少失而能亟反之者也。陈氏之说。似本于此。大抵气阳而质阴。气动而质静。气无形而质有体。凡人之耳目聪明。筋骸坚刚。质之粹者也。知觉妙运。思虑精当。气之清者也。古人之论魂魄。其义可见。夫魂者气之灵也。魄者质之灵也。若知魂魄之有二义。则气质知行之别。亦将一例推之而无疑矣。(朱子曰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虽然气至清者质无不粹。质至粹者气无不清。此章所谓知者虽曰气清而未免有所蔽。所谓贤者虽曰质粹而未免有所杂。不然何以有过不及之弊乎。○按栗谷言气质亦取陈意。见圣学辑要矫气质章。
或问二十章。亦尝分而言之。盖其论生知安行则曰禀气清明。赋质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丧者也。其论学知利行则曰得清之多而不能无蔽。得粹之多而不能无杂。天理少失而能亟反之者也。陈氏之说。似本于此。大抵气阳而质阴。气动而质静。气无形而质有体。凡人之耳目聪明。筋骸坚刚。质之粹者也。知觉妙运。思虑精当。气之清者也。古人之论魂魄。其义可见。夫魂者气之灵也。魄者质之灵也。若知魂魄之有二义。则气质知行之别。亦将一例推之而无疑矣。(朱子曰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虽然气至清者质无不粹。质至粹者气无不清。此章所谓知者虽曰气清而未免有所蔽。所谓贤者虽曰质粹而未免有所杂。不然何以有过不及之弊乎。○按栗谷言气质亦取陈意。见圣学辑要矫气质章。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欤条注。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
此善字与择善之善字有间。盖择善之善。专以合中者言。此所谓善。兼合中与不合中者而言。如诗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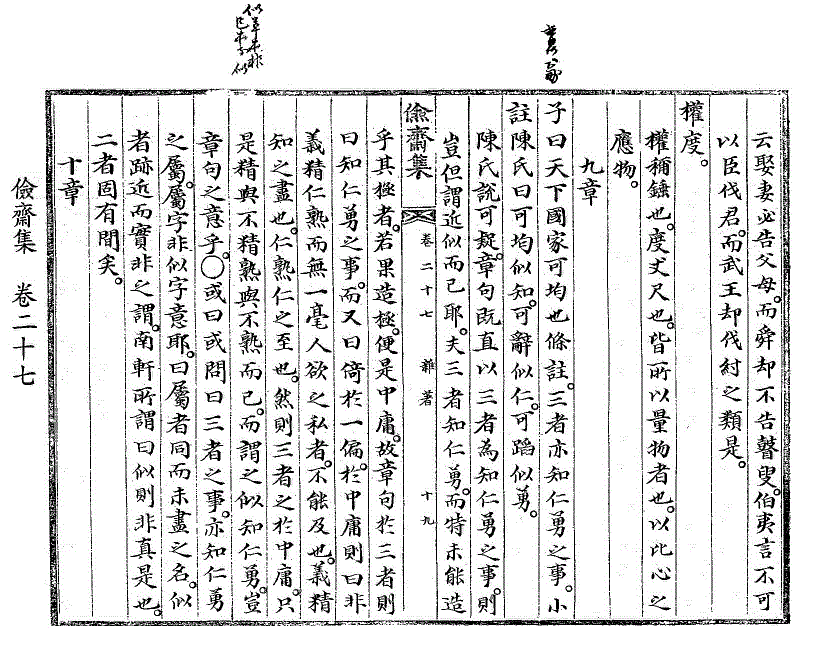 云娶妻必告父母。而舜却不告𥌒叟。伯夷言不可以臣伐君。而武王却伐纣之类是。
云娶妻必告父母。而舜却不告𥌒叟。伯夷言不可以臣伐君。而武王却伐纣之类是。权度。
权称锤也。度丈尺也。皆所以量物者也。以比心之应物。
九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条注。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小注陈氏曰可均似知。可辞似仁。可蹈似勇。
陈氏说可疑。章句既直以三者为知仁勇之事。则岂但谓近似而已耶。夫三者知仁勇。而特未能造乎其极者。若果造极。便是中庸。故章句于三者则曰知仁勇之事。而又曰倚于一偏。于中庸则曰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义精知之尽也。仁熟仁之至也。然则三者之于中庸。只是精与不精熟与不熟而已。而谓之似知仁勇。岂章句之意乎。○或曰或问曰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属。属字非似字意耶。曰属者同而未尽之名。似者迹近而实非之谓。南轩所谓曰似则非真是也。二者固有间矣。
十章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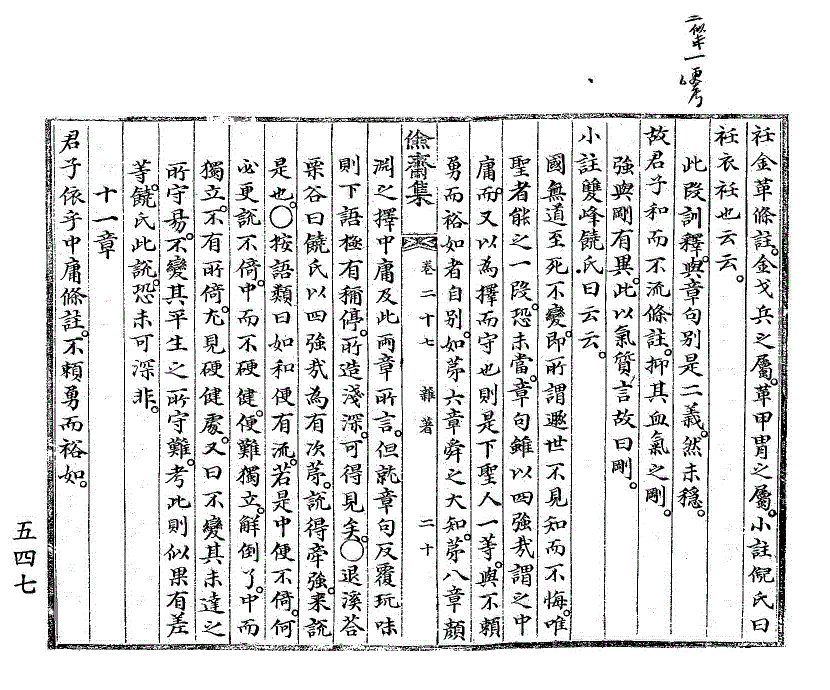 衽金革条注。金戈兵之属。革甲冑之属。小注倪氏曰衽衣衽也云云。
衽金革条注。金戈兵之属。革甲冑之属。小注倪氏曰衽衣衽也云云。此段训释。与章句别是二义。然未稳。
故君子和而不流条注。抑其血气之刚。
强与刚有异。此以气质言故曰刚。
小注双峰饶氏曰云云。
国无道至死不变。即所谓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一段。恐未当。章句虽以四强哉谓之中庸。而又以为择而守也则是下圣人一等。与不赖勇而裕如者自别。如第六章舜之大知。第八章颜渊之择中庸及此两章所言。但就章句反覆玩味则下语极有称停。所造浅深。可得见矣。○退溪答栗谷曰饶氏以四强哉为有次第。说得牵强。来说是也。○按语类曰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不倚。何必更说不倚。中而不硬健。便难独立。解倒了。中而独立。不有所倚。尤见硬健处。又曰不变其未达之所守易。不变其平生之所守难。考此则似果有差等。饶氏此说。恐未可深非。
十一章
君子依乎中庸条注。不赖勇而裕如。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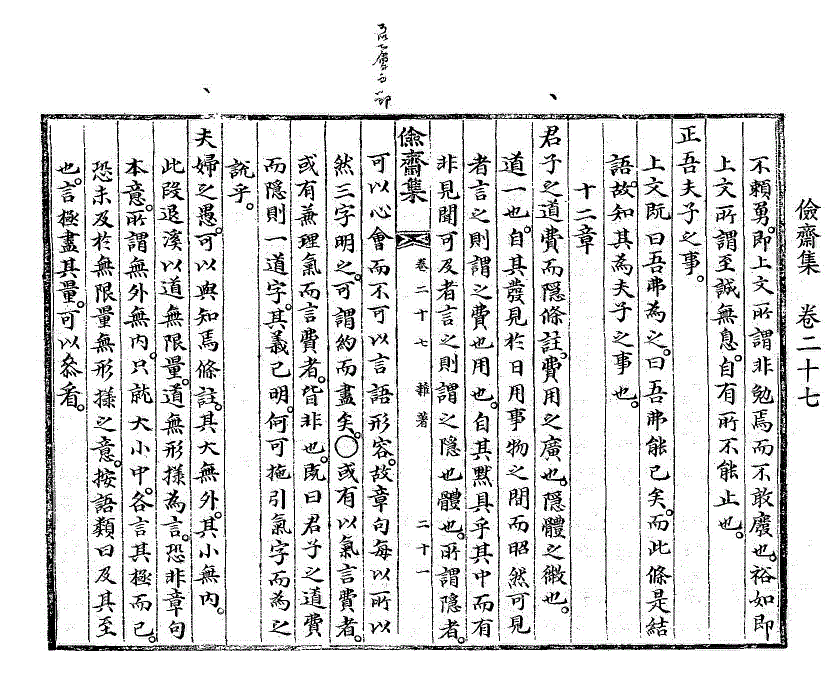 不赖勇。即上文所谓非勉焉而不敢废也。裕如即上文所谓至诚无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不赖勇。即上文所谓非勉焉而不敢废也。裕如即上文所谓至诚无息。自有所不能止也。正吾夫子之事。
上文既曰吾弗为之。曰吾弗能已矣。而此条是结语。故知其为夫子之事也。
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条注。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
道一也。自其发见于日用事物之间而昭然可见者言之则谓之费也用也。自其默具乎其中而有非见闻可及者言之则谓之隐也体也。所谓隐者。可以心会而不可以言语形容。故章句每以所以然三字明之。可谓约而尽矣。○或有以气言费者。或有兼理气而言费者。皆非也。既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则一道字。其义已明。何可拖引气字而为之说乎。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条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此段退溪以道无限量。道无形㨾为言。恐非章句本意。所谓无外无内。只就大小中。各言其极而已。恐未及于无限量无形㨾之意。按语类曰及其至也。言极尽其量。可以参看。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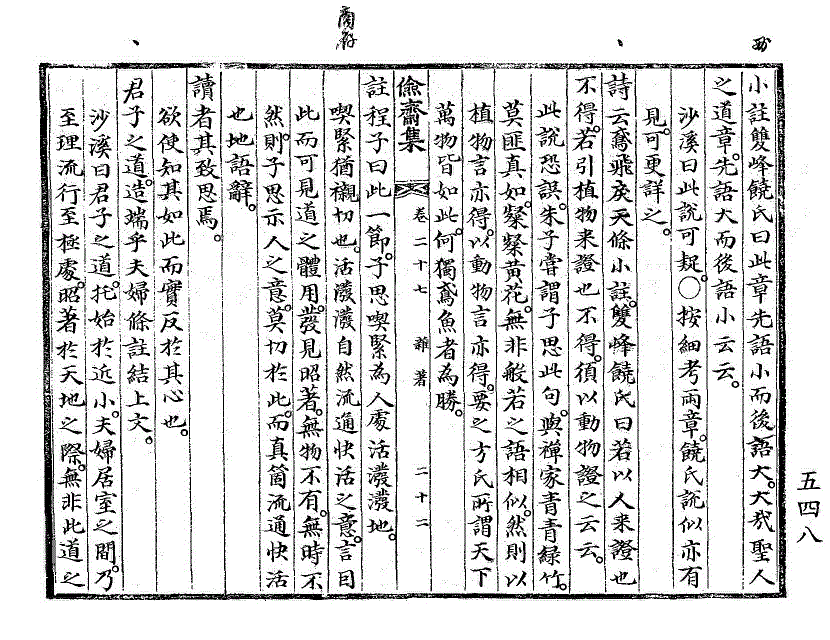 小注双峰饶氏曰此章先语小而后语大。大哉圣人之道章。先语大而后语小云云。
小注双峰饶氏曰此章先语小而后语大。大哉圣人之道章。先语大而后语小云云。沙溪曰此说可疑。○按细考两章。饶氏说似亦有见。可更详之。
诗云鸢飞戾天条小注。双峰饶氏曰若以人来證也不得。若引植物来證也不得。须以动物證之云云。
此说恐误。朱子尝谓子思此句。与禅家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之语相似。然则以植物言亦得。以动物言亦得。要之方氏所谓天下万物皆如此。何独鸢鱼者为胜。
注程子曰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
吃紧犹衬切也。活泼泼自然流通快活之意。言因此而可见道之体用。发见昭著。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则子思示人之意。莫切于此。而真个流通快活也。地语辞。
读者其致思焉。
欲使知其如此而实反于其心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条注结上文。
沙溪曰君子之道。托始于近小。夫妇居室之间。乃至理流行至极处。昭著于天地之际。无非此道之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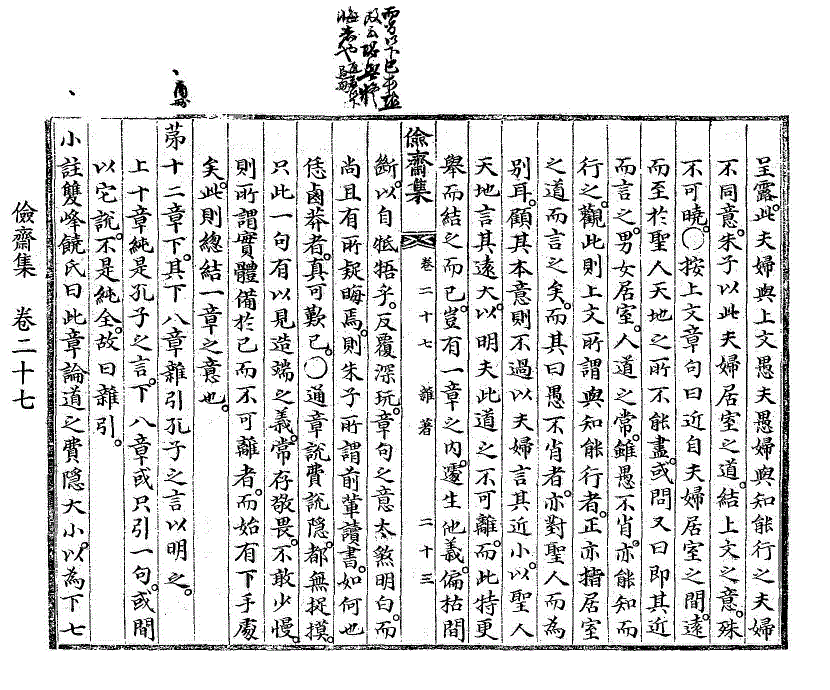 呈露。此夫妇与上文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之夫妇不同意。朱子以此夫妇居室之道。结上文之意。殊不可晓。○按上文章句曰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或问又曰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虽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观此则上文所谓与知能行者。正亦指居室之道而言之矣。而其曰愚不肖者。亦对圣人而为别耳。顾其本意则不过以夫妇言其近小。以圣人天地言其远大。以明夫此道之不可离。而此特更举而结之而已。岂有一章之内。遽生他义。偏枯间断。以自牴牾乎。反覆深玩。章句之意太煞明白。而尚且有所疑晦焉。则朱子所谓前辈读书。如何也恁卤莽者。真可叹已。○通章说费说隐。都无捉摸。只此一句有以见造端之义。常存敬畏。不敢少慢。则所谓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者。而始有下手处矣。此则总结一章之意也。
呈露。此夫妇与上文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之夫妇不同意。朱子以此夫妇居室之道。结上文之意。殊不可晓。○按上文章句曰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或问又曰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虽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观此则上文所谓与知能行者。正亦指居室之道而言之矣。而其曰愚不肖者。亦对圣人而为别耳。顾其本意则不过以夫妇言其近小。以圣人天地言其远大。以明夫此道之不可离。而此特更举而结之而已。岂有一章之内。遽生他义。偏枯间断。以自牴牾乎。反覆深玩。章句之意太煞明白。而尚且有所疑晦焉。则朱子所谓前辈读书。如何也恁卤莽者。真可叹已。○通章说费说隐。都无捉摸。只此一句有以见造端之义。常存敬畏。不敢少慢。则所谓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者。而始有下手处矣。此则总结一章之意也。第十二章下。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上十章纯是孔子之言。下八章或只引一句。或间以它说。不是纯全。故曰杂引。
小注双峰饶氏曰此章论道之费隐大小。以为下七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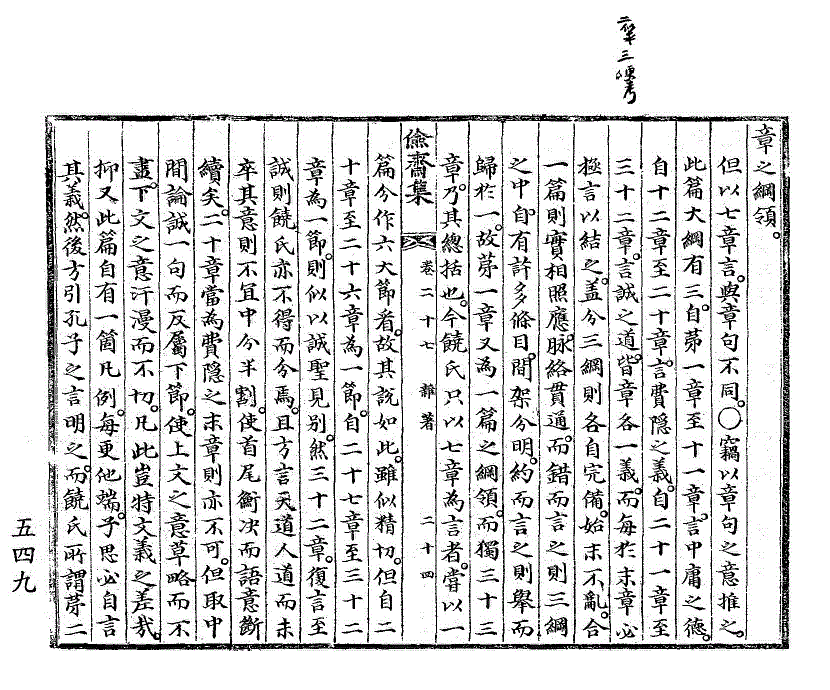 章之纲领。
章之纲领。但以七章言。与章句不同。○窃以章句之意推之。此篇大纲有三。自第一章至十一章。言中庸之德。自十二章至二十章。言费隐之义。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言诚之道。皆章各一义。而每于末章必极言以结之。盖分三纲则各自完备。始末不乱。合一篇则实相照应。脉络贯通。而错而言之则三纲之中。自有许多条目。间架分明。约而言之则举而归于一。故第一章又为一篇之纲领。而独三十三章。乃其总括也。今饶氏只以七章为言者。尝以一篇分作六大节看。故其说如此。虽似精切。但自二十章至二十六章为一节。自二十七章至三十二章为一节。则似以诚圣见别。然三十二章。复言至诚则饶氏亦不得而分焉。且方言天道人道而未卒其意则不宜中分半割。使首尾衡决而语意断续矣。二十章当为费隐之末章则亦不可。但取中间论诚一句而反属下节。使上文之意草略而不尽。下文之意汗漫而不切。凡此岂特文义之差哉。抑又此篇自有一个凡例。每更他端。子思必自言其义。然后方引孔子之言明之。而饶氏所谓第二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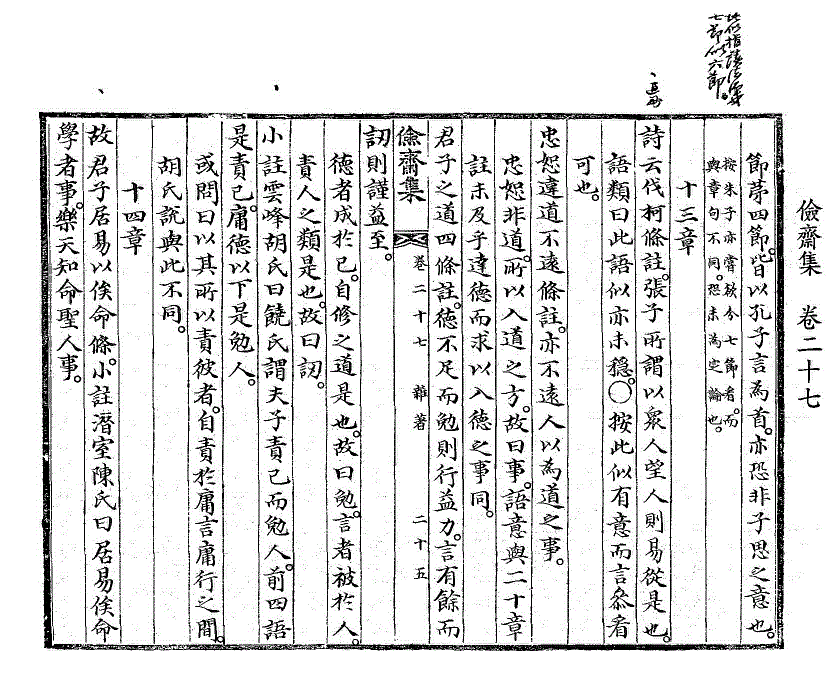 节第四节。皆以孔子言为首。亦恐非子思之意也。(按朱子亦尝欲分七节看。而与章句不同。恐未为定论也。)
节第四节。皆以孔子言为首。亦恐非子思之意也。(按朱子亦尝欲分七节看。而与章句不同。恐未为定论也。)十三章
诗云伐柯条注。张子所谓以众人望人则易从是也。
语类曰此语似亦未稳。○按此似有意而言参看可也。
忠恕违道不远条注。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
忠恕非道。所以入道之方。故曰事。语意与二十章注未及乎达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同。
君子之道四条注。德不足而勉则行益力。言有馀而讱则谨益至。
德者成于己。自修之道是也。故曰勉。言者被于人。责人之类是也。故曰讱。
小注云峰胡氏曰饶氏谓夫子责己而勉人。前四语是责己。庸德以下是勉人。
或问曰以其所以责彼者。自责于庸言庸行之间。胡氏说与此不同。
十四章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条。小注潜室陈氏曰居易俟命学者事。乐天知命圣人事。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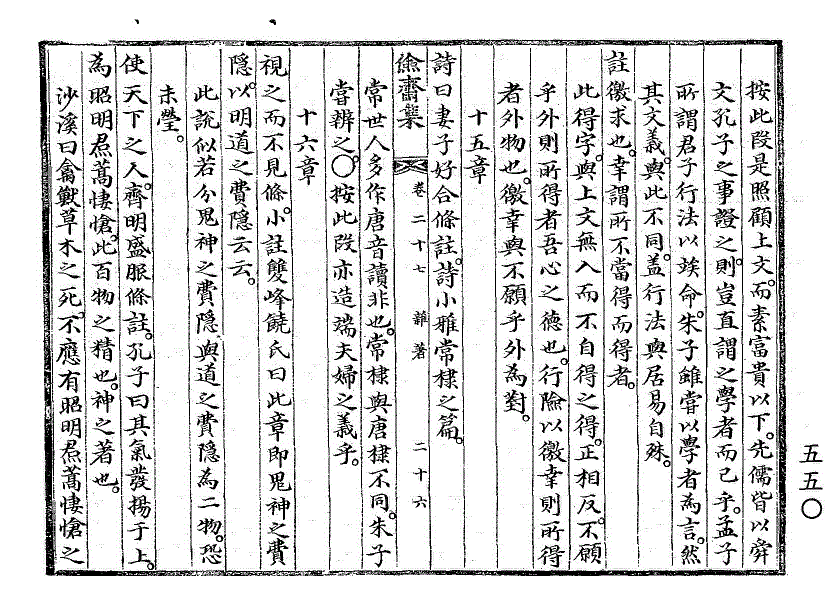 按此段是照顾上文。而素富贵以下。先儒皆以舜文孔子之事證之。则岂直谓之学者而已乎。孟子所谓君子行法以俟命。朱子虽尝以学者为言。然其文义。与此不同。盖行法与居易自殊。
按此段是照顾上文。而素富贵以下。先儒皆以舜文孔子之事證之。则岂直谓之学者而已乎。孟子所谓君子行法以俟命。朱子虽尝以学者为言。然其文义。与此不同。盖行法与居易自殊。注徼求也。幸谓所不当得而得者。
此得字。与上文无入而不自得之得。正相反。不愿乎外则所得者吾心之德也。行险以徼幸则所得者外物也。徼幸与不愿乎外为对。
十五章
诗曰妻子好合条注。诗小雅常棣之篇。
常世人多作唐音读非也。常棣与唐棣不同。朱子尝辨之。○按此段亦造端夫妇之义乎。
十六章
视之而不见条。小注双峰饶氏曰此章即鬼神之费隐。以明道之费隐云云。
此说似若分鬼神之费隐与道之费隐为二物。恐未莹。
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条注。孔子曰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悽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沙溪曰禽兽草木之死。不应有昭明焄蒿悽怆之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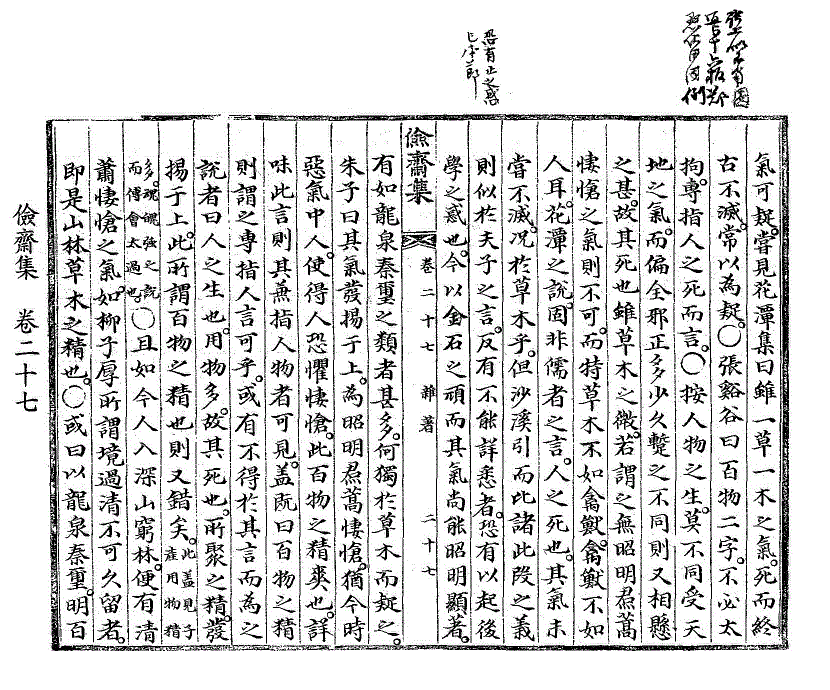 气可疑。尝见花潭集曰虽一草一木之气。死而终古不灭。常以为疑。○张溪谷曰百物二字。不必太拘。专指人之死而言。○按人物之生。莫不同受天地之气。而偏全邪正多少久暂之不同则又相悬之甚。故其死也虽草木之微。若谓之无昭明焄蒿悽怆之气则不可。而特草木不如禽兽。禽兽不如人耳。花潭之说。固非儒者之言。人之死也。其气未尝不灭。况于草木乎。但沙溪引而比诸此段之义则似于夫子之言。反有不能详悉者。恐有以起后学之惑也。今以金石之顽而其气尚能昭明显著。有如龙泉秦玺之类者甚多。何独于草木而疑之。朱子曰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悽怆。犹今时恶气中人。使得人恐惧悽怆。此百物之精爽也。详味此言则其兼指人物者可见。盖既曰百物之精则谓之专指人言可乎。或有不得于其言而为之说者曰人之生也。用物多。故其死也。所聚之精。发扬于上。此所谓百物之精也则又错矣。(此盖见子产用物精多。魂魄强之说而傅会太过也。)○且如今人入深山穷林。便有清萧悽怆之气。如柳子厚所谓境过清不可久留者。即是山林草木之精也。○或曰以龙泉秦玺。明百
气可疑。尝见花潭集曰虽一草一木之气。死而终古不灭。常以为疑。○张溪谷曰百物二字。不必太拘。专指人之死而言。○按人物之生。莫不同受天地之气。而偏全邪正多少久暂之不同则又相悬之甚。故其死也虽草木之微。若谓之无昭明焄蒿悽怆之气则不可。而特草木不如禽兽。禽兽不如人耳。花潭之说。固非儒者之言。人之死也。其气未尝不灭。况于草木乎。但沙溪引而比诸此段之义则似于夫子之言。反有不能详悉者。恐有以起后学之惑也。今以金石之顽而其气尚能昭明显著。有如龙泉秦玺之类者甚多。何独于草木而疑之。朱子曰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悽怆。犹今时恶气中人。使得人恐惧悽怆。此百物之精爽也。详味此言则其兼指人物者可见。盖既曰百物之精则谓之专指人言可乎。或有不得于其言而为之说者曰人之生也。用物多。故其死也。所聚之精。发扬于上。此所谓百物之精也则又错矣。(此盖见子产用物精多。魂魄强之说而傅会太过也。)○且如今人入深山穷林。便有清萧悽怆之气。如柳子厚所谓境过清不可久留者。即是山林草木之精也。○或曰以龙泉秦玺。明百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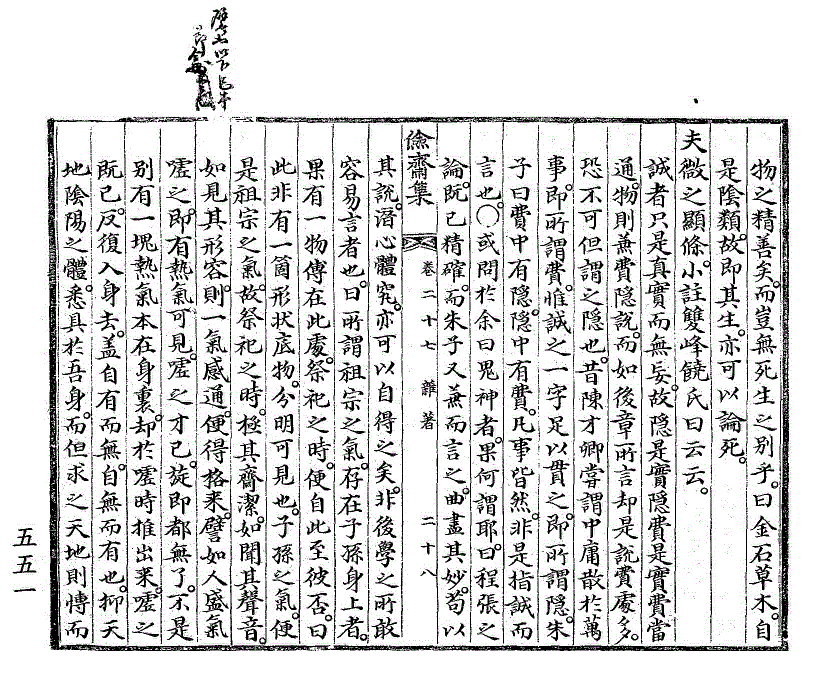 物之精善矣。而岂无死生之别乎。曰金石草木。自是阴类。故即其生。亦可以论死。
物之精善矣。而岂无死生之别乎。曰金石草木。自是阴类。故即其生。亦可以论死。夫微之显条。小注双峰饶氏曰云云。
诚者只是真实而无妄。故隐是实隐费是实费当通。物则兼费隐说。而如后章所言却是说费处多。恐不可但谓之隐也。昔陈才卿尝谓中庸散于万事。即所谓费。惟诚之一字足以贯之。即所谓隐。朱子曰费中有隐。隐中有费。凡事皆然。非是指诚而言也。○或问于余曰鬼神者。果何谓耶。曰程张之论。既已精确。而朱子又兼而言之。曲尽其妙。苟以其说。潜心体究。亦可以自得之矣。非后学之所敢容易言者也。曰所谓祖宗之气。存在子孙身上者。果有一物傅在此处。祭祀之时。便自此至彼否。曰此非有一个形状底物。分明可见也。子孙之气。便是祖宗之气。故祭祀之时。极其斋洁。如闻其声音。如见其形容。则一气感通。便得格来。譬如人盛气嘘之。即有热气可见。嘘之才已。旋即都无了。不是别有一块热气本在身里。却于嘘时推出来。嘘之既已。反复入身去。盖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也。抑天地阴阳之体。悉具于吾身。而但求之天地则博而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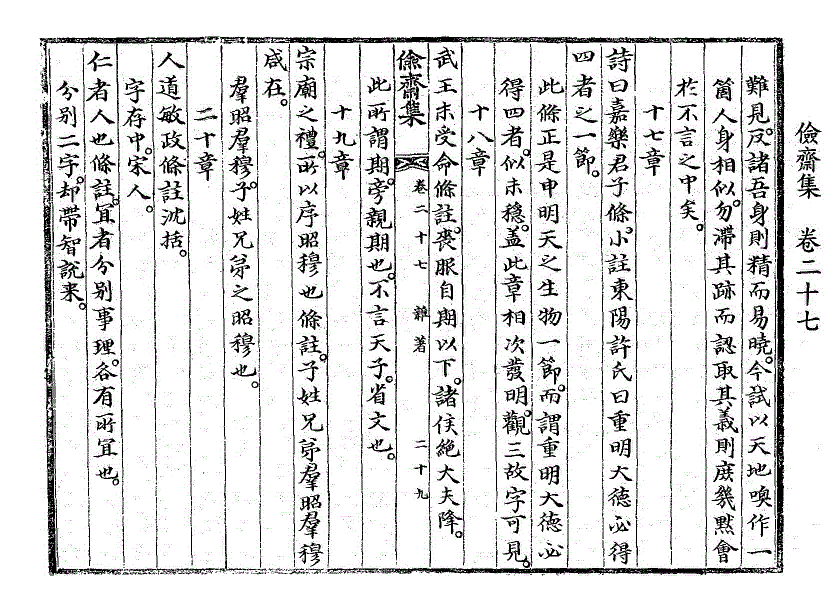 难见。反诸吾身则精而易晓。今试以天地唤作一个人身相似。勿滞其迹而认取其义则庶几默会于不言之中矣。
难见。反诸吾身则精而易晓。今试以天地唤作一个人身相似。勿滞其迹而认取其义则庶几默会于不言之中矣。十七章
诗曰嘉乐君子条。小注东阳许氏曰重明大德必得四者之一节。
此条正是申明天之生物一节。而谓重明大德必得四者。似未稳。盖此章相次发明。观三故字可见。
十八章
武王末受命条注。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
此所谓期。旁亲期也。不言天子。省文也。
十九章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条注。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
群昭群穆。子姓兄弟之昭穆也。
二十章
人道敏政条注沈括。
字存中。宋人。
仁者人也条注。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
分别二字。却带智说来。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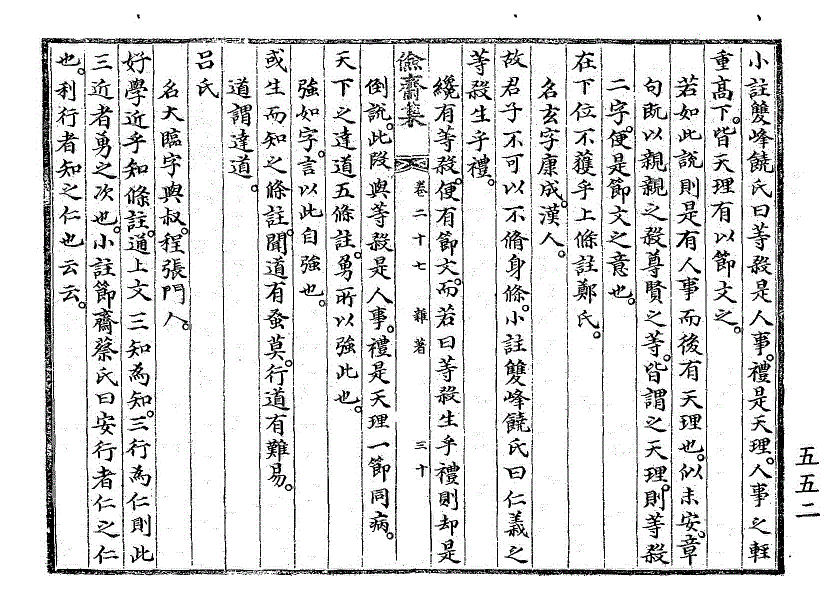 小注双峰饶氏曰等杀是人事。礼是天理。人事之轻重高下。皆天理有以节文之。
小注双峰饶氏曰等杀是人事。礼是天理。人事之轻重高下。皆天理有以节文之。若如此说则是有人事而后有天理也。似未安。章句既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谓之天理。则等杀二字。便是节文之意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条注郑氏。
名玄字康成。汉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条。小注双峰饶氏曰仁义之等杀生乎礼。
才有等杀。便有节文。而若曰等杀生乎礼则却是倒说。此段与等杀是人事。礼是天理一节同病。
天下之达道五条注。勇所以强此也。
强如字。言以此自强也。
或生而知之条注。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
道谓达道。
吕氏。
名大临字与叔。程张门人。
好学近乎知条注。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则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小注节斋蔡氏曰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云云。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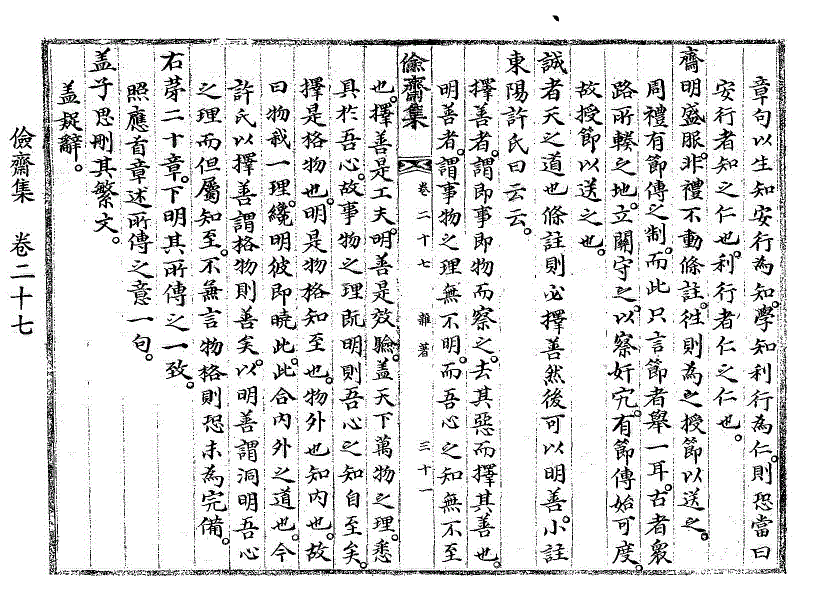 章句以生知安行为知。学知利行为仁。则恐当曰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
章句以生知安行为知。学知利行为仁。则恐当曰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条注。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
周礼有节传之制。而此只言节者举一耳。古者众路所辏之地。立关守之。以察奸宄。有节传始可度。故授节以送之也。
诚者天之道也条注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小注东阳许氏曰云云。
择善者。谓即事即物而察之。去其恶而择其善也。明善者。谓事物之理无不明。而吾心之知无不至也。择善是工夫。明善是效验。盖天下万物之理。悉具于吾心。故事物之理既明则吾心之知自至矣。择是格物也。明是物格知至也。物外也知内也。故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今许氏以择善谓格物则善矣。以明善谓洞明吾心之理而但属知至。不兼言物格则恐未为完备。
右第二十章。下明其所传之一致。
照应首章述所传之意一句。
盖子思删其繁文。
盖疑辞。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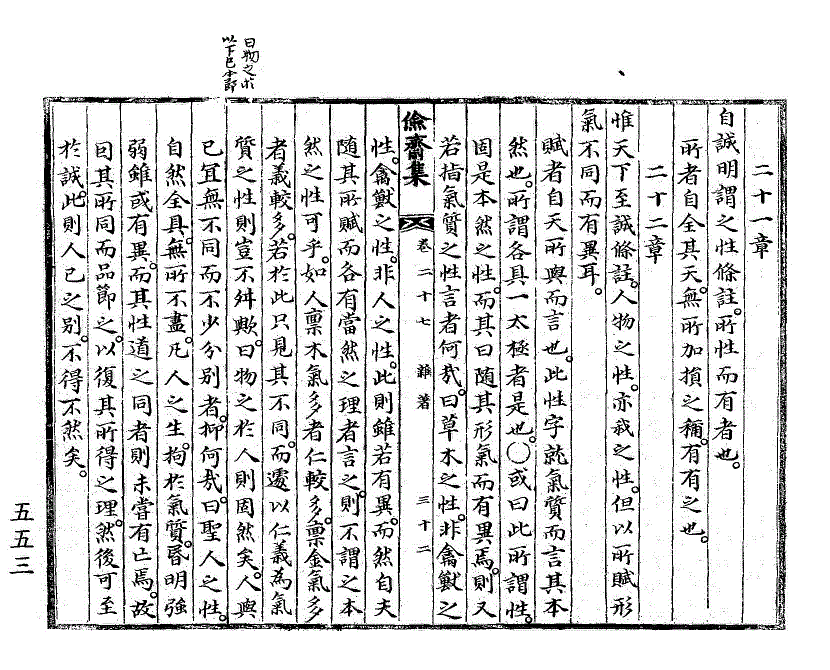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条注。所性而有者也。
所者自全其天。无所加损之称。有有之也。
二十二章
惟天下至诚条注。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
赋者自天所与而言也。此性字就气质而言其本然也。所谓各具一太极者是也。○或曰此所谓性。固是本然之性。而其曰随其形气而有异焉。则又若指气质之性言者何哉。曰草木之性。非禽兽之性。禽兽之性。非人之性。此则虽若有异。而然自夫随其所赋而各有当然之理者言之。则不谓之本然之性可乎。如人禀木气多者仁较多。禀金气多者义较多。若于此只见其不同。而遽以仁义为气质之性则岂不舛欤。曰物之于人则固然矣。人与己宜无不同而不少分别者。抑何哉。曰圣人之性。自然全具。无所不尽。凡人之生。拘于气质。昏明强弱虽或有异。而其性道之同者则未尝有亡焉。故因其所同而品节之。以复其所得之理。然后可至于诚。此则人己之别。不得不然矣。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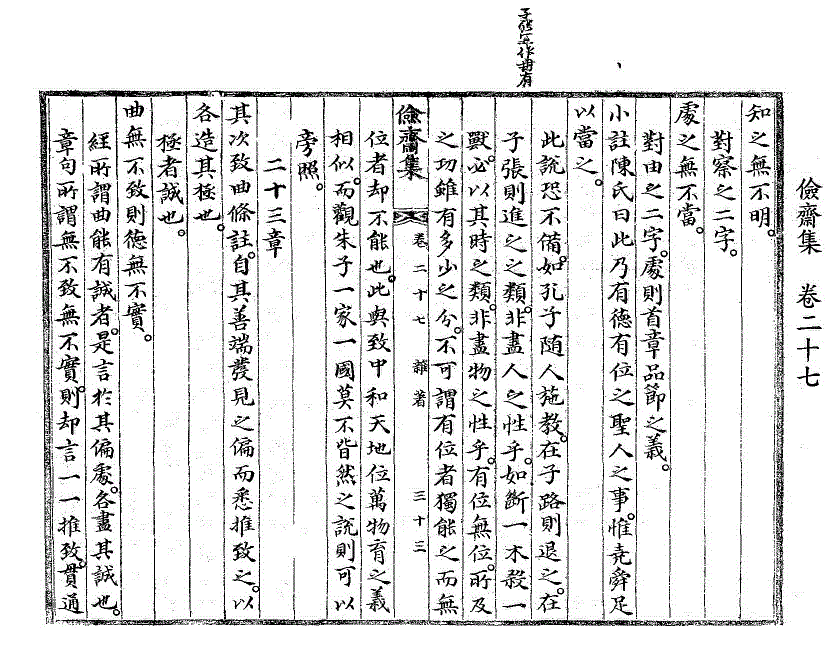 知之无不明。
知之无不明。对察之二字。
处之无不当。
对由之二字。处则首章品节之义。
小注陈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圣人之事。惟尧舜足以当之。
此说恐不备。如孔子随人施教。在子路则退之。在子张则进之之类。非尽人之性乎。如断一木杀一兽。必以其时之类。非尽物之性乎。有位无位。所及之功虽有多少之分。不可谓有位者独能之而无位者却不能也。此与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之义相似。而观朱子一家一国莫不皆然之说则可以旁照。
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条注。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
极者诚也。
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
经所谓曲能有诚者。是言于其偏处。各尽其诚也。章句所谓无不致无不实。则却言一一推致。贯通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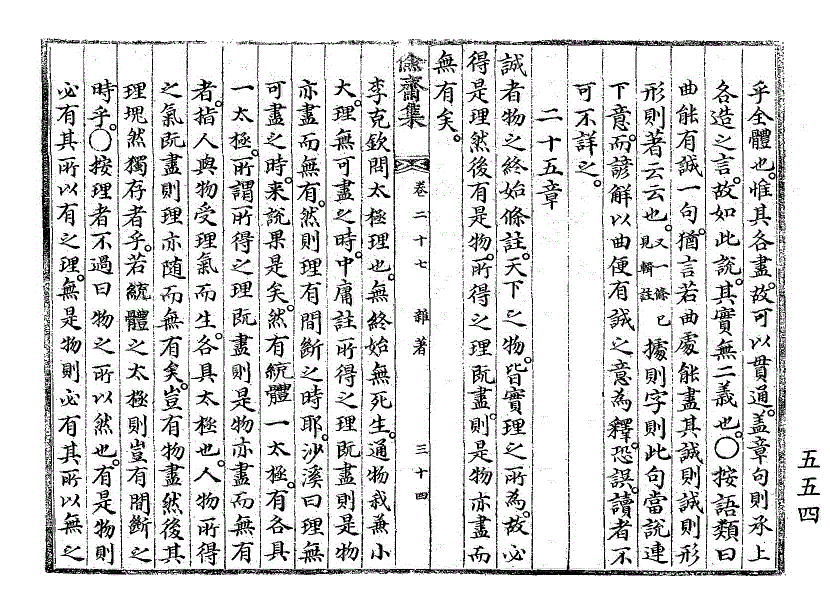 乎全体也。惟其各尽。故可以贯通。盖章句则承上各造之言。故如此说。其实无二义也。○按语类曰曲能有诚一句。犹言若曲处能尽其诚则诚则形形则著云云也。(又一条已见辑注。)据则字则此句当说连下意。而谚解以曲便有诚之意为释。恐误。读者不可不详之。
乎全体也。惟其各尽。故可以贯通。盖章句则承上各造之言。故如此说。其实无二义也。○按语类曰曲能有诚一句。犹言若曲处能尽其诚则诚则形形则著云云也。(又一条已见辑注。)据则字则此句当说连下意。而谚解以曲便有诚之意为释。恐误。读者不可不详之。二十五章
诚者物之终始条注。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
李克钦问太极理也。无终始无死生。通物我兼小大。理无可尽之时。中庸注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然则理有间断之时耶。沙溪曰理无可尽之时。来说果是矣。然有统体一太极。有各具一太极。所谓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者。指人与物受理气而生。各具太极也。人物所得之气既尽则理亦随而无有矣。岂有物尽然后其理块然独存者乎。若统体之太极则岂有间断之时乎。○按理者不过曰物之所以然也。有是物则必有其所以有之理。无是物则必有其所以无之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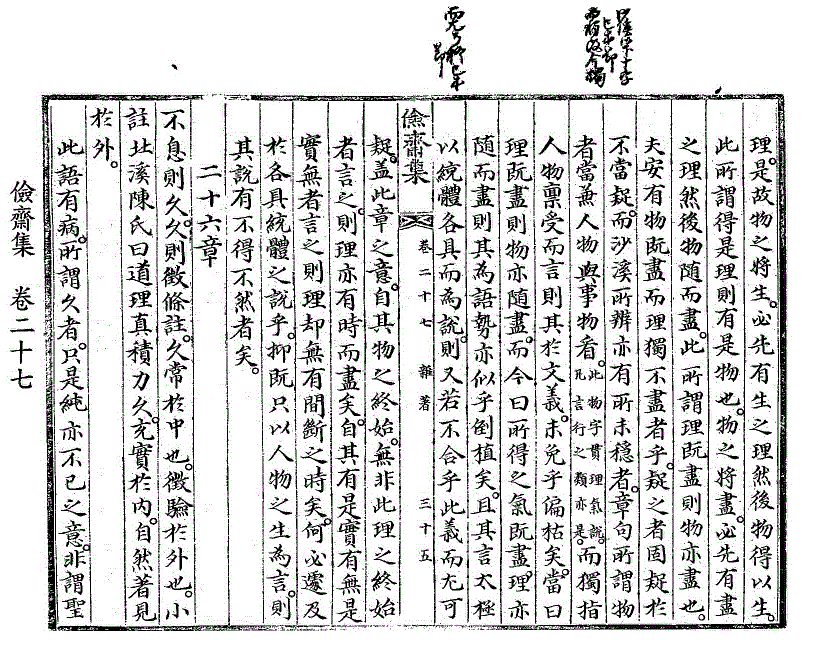 理。是故物之将生。必先有生之理然后物得以生。此所谓得是理则有是物也。物之将尽。必先有尽之理然后物随而尽。此所谓理既尽则物亦尽也。夫安有物既尽而理独不尽者乎。疑之者固疑于不当疑。而沙溪所辨亦有所未稳者。章句所谓物者当兼人物与事物看。(此物字贯理气说。凡言行之类亦是。)而独指人物禀受而言则其于文义。未免乎偏枯矣。当曰理既尽则物亦随尽。而今曰所得之气既尽。理亦随而尽则其为语势亦似乎倒植矣。且其言太极以统体各具而为说。则又若不合乎此义而尤可疑。盖此章之意。自其物之终始。无非此理之终始者言之。则理亦有时而尽矣。自其有是实有无是实无者言之则理却无有间断之时矣。何必遽及于各具统体之说乎。抑既只以人物之生为言。则其说有不得不然者矣。
理。是故物之将生。必先有生之理然后物得以生。此所谓得是理则有是物也。物之将尽。必先有尽之理然后物随而尽。此所谓理既尽则物亦尽也。夫安有物既尽而理独不尽者乎。疑之者固疑于不当疑。而沙溪所辨亦有所未稳者。章句所谓物者当兼人物与事物看。(此物字贯理气说。凡言行之类亦是。)而独指人物禀受而言则其于文义。未免乎偏枯矣。当曰理既尽则物亦随尽。而今曰所得之气既尽。理亦随而尽则其为语势亦似乎倒植矣。且其言太极以统体各具而为说。则又若不合乎此义而尤可疑。盖此章之意。自其物之终始。无非此理之终始者言之。则理亦有时而尽矣。自其有是实有无是实无者言之则理却无有间断之时矣。何必遽及于各具统体之说乎。抑既只以人物之生为言。则其说有不得不然者矣。二十六章
不息则久。久则徵条注。久常于中也。徵验于外也。小注北溪陈氏曰道理真积力久。充实于内。自然著见于外。
此语有病。所谓久者。只是纯亦不已之意。非谓圣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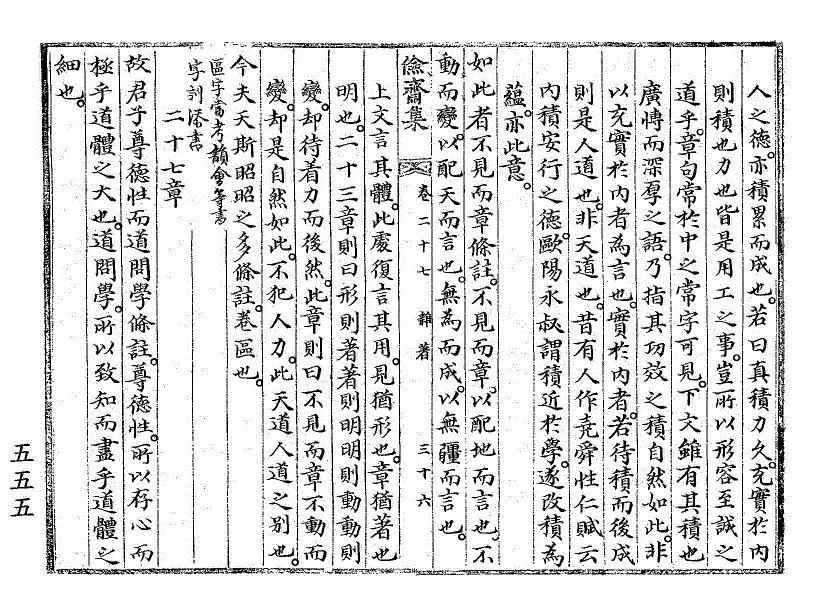 人之德。亦积累而成也。若曰真积力久。充实于内则积也力也皆是用工之事。岂所以形容至诚之道乎。章句常于中之常字可见。下文虽有其积也广博而深厚之语。乃指其功效之积自然如此。非以充实于内者为言也。实于内者。若待积而后成则是人道也。非天道也。昔有人作尧舜性仁赋云内积安行之德。欧阳永叔谓积近于学。遂改积为蕴。亦此意。
人之德。亦积累而成也。若曰真积力久。充实于内则积也力也皆是用工之事。岂所以形容至诚之道乎。章句常于中之常字可见。下文虽有其积也广博而深厚之语。乃指其功效之积自然如此。非以充实于内者为言也。实于内者。若待积而后成则是人道也。非天道也。昔有人作尧舜性仁赋云内积安行之德。欧阳永叔谓积近于学。遂改积为蕴。亦此意。如此者不见而章条注。不见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动而变。以配天而言也。无为而成。以无疆而言也。
上文言其体。此处复言其用。见犹形也。章犹著也明也。二十三章则曰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却待着力而后然。此章则曰不见而章不动而变。却是自然如此。不犯人力。此天道人道之别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条注。卷区也。
二十七章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条注。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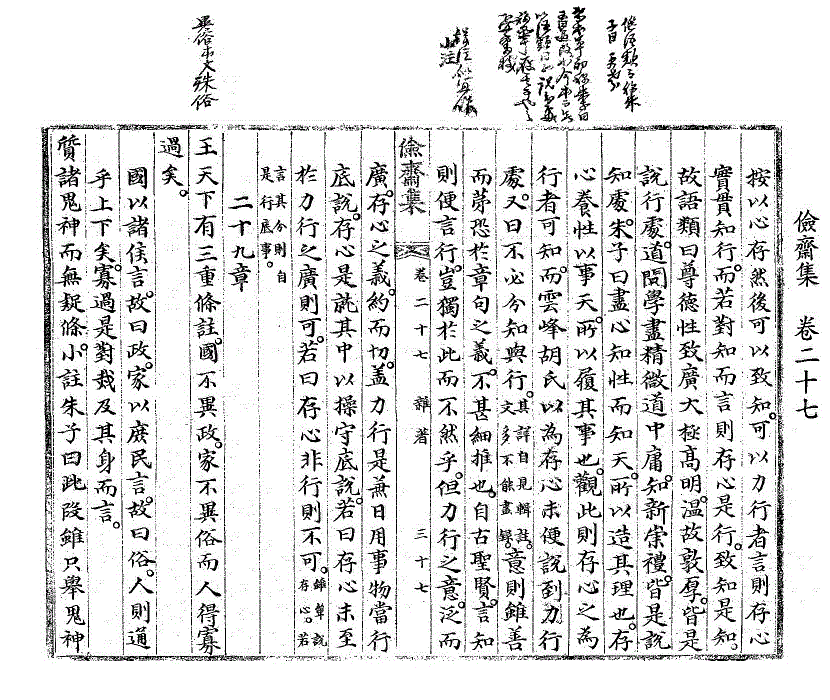 按以心存然后可以致知。可以力行者言则存心实贯知行。而若对知而言则存心是行。致知是知。故语类曰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皆是说行处。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皆是说知处。朱子曰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观此则存心之为行者可知。而云峰胡氏以为存心未便说到力行处。又曰不必分知与行。(其详自见辑注。文多不能尽录。)意则虽善而第恐于章句之义。不甚细推也。自古圣贤。言知则便言行。岂独于此而不然乎。但力行之意。泛而广。存心之义。约而切。盖力行是兼日用事物当行底说。存心是就其中以操守底说。若曰存心未至于力行之广则可。若曰存心非行则不可。(虽单说存心。若言其分则自是行底事。)
按以心存然后可以致知。可以力行者言则存心实贯知行。而若对知而言则存心是行。致知是知。故语类曰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皆是说行处。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皆是说知处。朱子曰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观此则存心之为行者可知。而云峰胡氏以为存心未便说到力行处。又曰不必分知与行。(其详自见辑注。文多不能尽录。)意则虽善而第恐于章句之义。不甚细推也。自古圣贤。言知则便言行。岂独于此而不然乎。但力行之意。泛而广。存心之义。约而切。盖力行是兼日用事物当行底说。存心是就其中以操守底说。若曰存心未至于力行之广则可。若曰存心非行则不可。(虽单说存心。若言其分则自是行底事。)二十九章
王天下有三重条注。国不异政。家不异俗而人得寡过矣。
国以诸侯言。故曰政。家以庶民言。故曰俗。人则通乎上下矣。寡过是对灾及其身而言。
质诸鬼神而无疑条。小注朱子曰此段虽只举鬼神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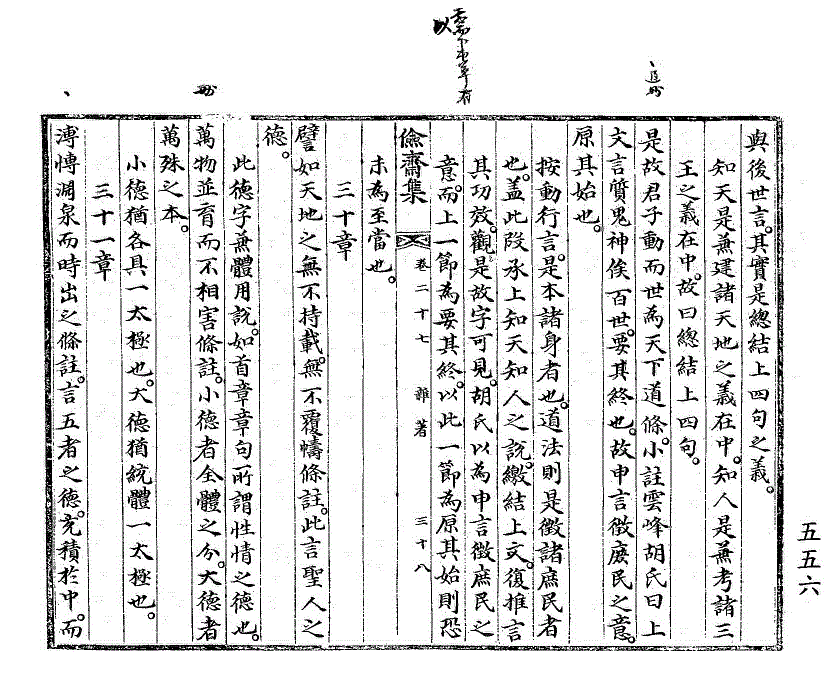 与后世言。其实是总结上四句之义。
与后世言。其实是总结上四句之义。知天是兼建诸天地之义在中。知人是兼考诸三王之义在中。故曰总结上四句。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条。小注云峰胡氏曰上文言质鬼神俟百世。要其终也。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按动行言。是本诸身者也。道法则是徵诸庶民者也。盖此段承上知天知人之说。缴结上文。复推言其功效。观是故字可见。胡氏以为申言徵庶民之意。而上一节为要其终。以此一节为原其始则恐未为至当也。
三十章
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条注。此言圣人之德。
此德字兼体用说。如首章章句所谓性情之德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条注。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
小德犹各具一太极也。大德犹统体一太极也。
三十一章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条注。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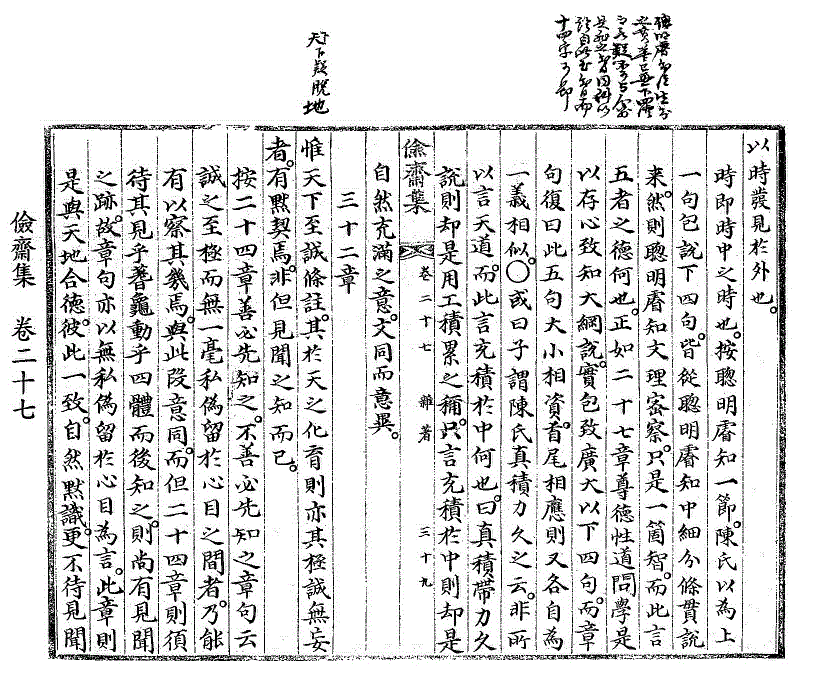 以时发见于外也。
以时发见于外也。时即时中之时也。按聪明睿知一节。陈氏以为上一句包说下四句。皆从聪明睿知中细分条贯说来。然则聪明睿知文理密察。只是一个智。而此言五者之德何也。正如二十七章尊德性道问学是以存心致知大纲说。实包致广大以下四句。而章句复曰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则又各自为一义相似。○或曰子谓陈氏真积力久之云。非所以言天道。而此言充积于中何也。曰真积带力久说则却是用工积累之称。只言充积于中则却是自然充满之意。文同而意异。
三十二章
惟天下至诚条注。其于天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见闻之知而已。
按二十四章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章句云诚之至极而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者。乃能有以察其几焉。与此段意同。而但二十四章则须待其见乎蓍龟动乎四体而后知之。则尚有见闻之迹。故章句亦以无私伪留于心目为言。此章则是与天地合德。彼此一致。自然默识。更不待见闻
俭斋集卷之二十七 第 5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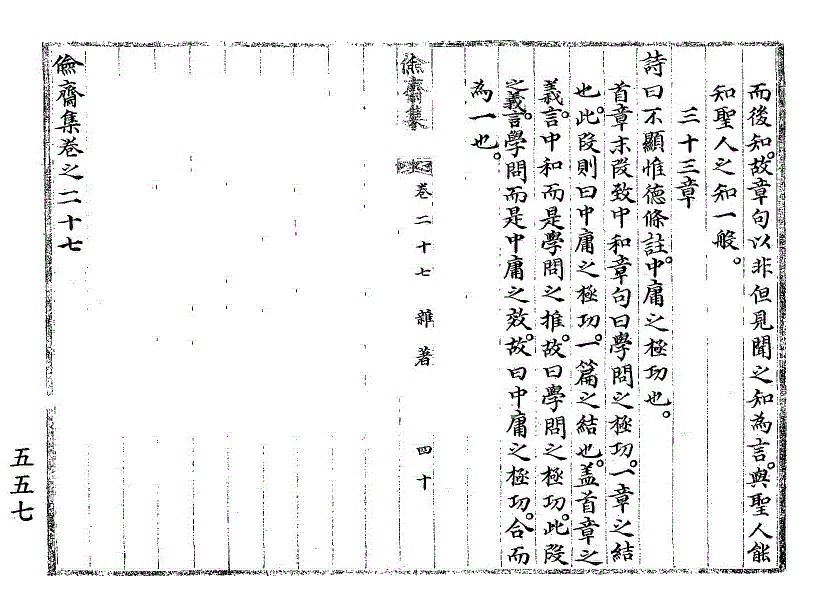 而后知。故章句以非但见闻之知为言。与圣人能知圣人之知一般。
而后知。故章句以非但见闻之知为言。与圣人能知圣人之知一般。三十三章
诗曰不显惟德条注。中庸之极功也。
首章末段致中和章句曰学问之极功。一章之结也。此段则曰中庸之极功。一篇之结也。盖首章之义。言中和而是学问之推。故曰学问之极功。此段之义。言学问而是中庸之效。故曰中庸之极功。合而为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