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x 页
俭斋集卷之十八
辨
辨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1H 页
 崔氏礼类册子辨
崔氏礼类册子辨(己丑礼类事后。先生著此拟进 睿览矣。未几有礼类焚书之 命。未果上。)
前领相崔锡鼎。既纷乱经文。改换章句。言者迭出而攻之。其所自解者。初则以为一字不为移动。中则又引王柏诸人以自比。而稍服其纷改之实。末乃作一册子以进。条辨人言而广引背异于朱子者。以自文饰。其言之荒诞闪忽。有足以荧惑 天听。而其曰一言半辞。违覆于朱门。则大忧以惧。若犯大讳。未免太伤于拘滞。又曰稍有差殊于传注则张目呵禁。惟恐触犯。又曰任世道之责者。何可一切严防。有若立法设禁者然哉。此其一篇主意也。盖 圣上于谏臣疏批。引其序文中一言一句。不敢删削之语。故其疏初出于牢讳之计。姑且以顺 上教。及夫言者发其实状。则乃不得已强引不当引之事。游辞陈章。而 圣批又不以二言见责无圣见诛。遂有以窥 天意而尚不敢显言己志。乃使薇垣之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1L 页
 长。投疏探试。且有勿捧儒疏之 教。然后始敢肆然以此言进。略无顾忌。乃尔。呜呼。世道至此。尚何言哉。所可惧者。人主所以处崇高而不敢肆。御万民而出治道者。岂有他哉。法经传也师圣贤也。而今乃以轻视先贤。蔑弃成训。导之于前。以阴坏其尊德乐道之诚。端本出治之原。其为祸岂特分裂篇章。汩陈文义而已哉。臣故为之辨。庶几有补于闲圣道息邪说之万一云。
长。投疏探试。且有勿捧儒疏之 教。然后始敢肆然以此言进。略无顾忌。乃尔。呜呼。世道至此。尚何言哉。所可惧者。人主所以处崇高而不敢肆。御万民而出治道者。岂有他哉。法经传也师圣贤也。而今乃以轻视先贤。蔑弃成训。导之于前。以阴坏其尊德乐道之诚。端本出治之原。其为祸岂特分裂篇章。汩陈文义而已哉。臣故为之辨。庶几有补于闲圣道息邪说之万一云。册子曰庸学篇题。既出朱子之撰定。语约意尽。诚如所云。若传誊本篇而已则何敢轻有变动。而今既遵仿通解。还编于礼记。则篇题体段。宜与礼经诸篇同例。盖朱子于通解诸篇。各著篇题。庸学二书。亦另具篇题。而其文与今刊行本之篇题。详略悬殊。文句亦异。今类编中二书篇题之删节。亦据此例耳。
辨曰此已是初头白撰之说也。按通解本篇篇题。与刊行本之篇题。无一字之差殊。覆视可验。今此详略悬殊。文句亦异之云。果何从而发耶。告君之辞。岂容若是其虚罔乎。(通解首卷目录。各篇下有略论大旨之言。而与篇题体例。大相不同。今虽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2H 页
 欲妆撰。必不敢以此谓之篇题矣。)今具载章句。且书之曰朱子章句而辄以己意句抹添删于其间。未知是朱子之章句耶。锡鼎之章句耶。其为僭妄。不待辨而明矣。(仪礼独非礼经耶。其篇题宁有不合于礼记篇题之理。而必为窜改乎。)
欲妆撰。必不敢以此谓之篇题矣。)今具载章句。且书之曰朱子章句而辄以己意句抹添删于其间。未知是朱子之章句耶。锡鼎之章句耶。其为僭妄。不待辨而明矣。(仪礼独非礼经耶。其篇题宁有不合于礼记篇题之理。而必为窜改乎。)册子曰大学篇题。初头添入十一字。礼经篇题之例。宜有解释名篇之语。而不敢遽自立说。谨用朱子序文中首句。剟取要旨。载于篇题之首曰。此篇记古者太学教人之法。通解篇题云专言古者太学教人之次第。序文首句语意相同。故取通解之意。存本序之文。所添入者。即朱子之说也。中庸篇题初头。删却十六字。乃篇目二字之注脚。故今行刊本与下文子程子之言。不为连书。别而二之。通解中庸篇内十六字为小注。子程子以下方为大字。其意不翅较然。而第二章注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篇目下注脚。不必复出而斯义已明。
辨曰大学篇题十一字之添入。若果取于通解或本序之文。则何不直载其文。而妄有所点窜耶。既是所自添删。则何不曰附注。而偃然滚入于章句之中而无所别也。朱子定其脱误云云。及本居儒行之下云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2L 页
 云等语。明是锡鼎之所自添。而亦系之于朱子章句之名。非但僭猥舛缪之甚。其于文义。亦不相照矣。中庸篇题十六字。乃朱子所自为者。与程子之言。条贯各异。又不欲以己说连书。加之于先辈之上。故区而别之者此也。按今刊本通解笺注皆小字也。以中庸章句言之。独子程子云云及章下数段之外。其他皆作小字。(三十章内。只五章作大字。以其一章而揔论数章之义故也。)若以小注而删之则章句一篇。皆将尽削矣。今以为其意不啻较然。果成说乎。(通解笺注之作小字。锡鼎亦岂不知。而今以此为言。诚莫知其意也。)且此十六字。乃开卷第一义。而其义之不明于世久矣。吕温胡广之中庸。皆出于不识此义。而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者。亦未足以尽其义。故特以此加之于篇首而著之于二章。又编之于通解。其丁宁反复为天下后世虑也深且切矣。今以为不必复出而一笔削去。此果知朱子之意而尊信严畏者耶。(孝经闺门章。不过二十二字。而司马贞削去之。识者以为卒启开元无礼之祸。圣贤之言。其可容易删减乎。)且大学篇题中。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十五字。及中庸篇题中恐其久而差也六字之删去。又何意也。岂差之一字。切中其忌讳。故不欲言之。如蔡京之讳言危亡乱字耶。朱夫子定著章句。自谓
云等语。明是锡鼎之所自添。而亦系之于朱子章句之名。非但僭猥舛缪之甚。其于文义。亦不相照矣。中庸篇题十六字。乃朱子所自为者。与程子之言。条贯各异。又不欲以己说连书。加之于先辈之上。故区而别之者此也。按今刊本通解笺注皆小字也。以中庸章句言之。独子程子云云及章下数段之外。其他皆作小字。(三十章内。只五章作大字。以其一章而揔论数章之义故也。)若以小注而删之则章句一篇。皆将尽削矣。今以为其意不啻较然。果成说乎。(通解笺注之作小字。锡鼎亦岂不知。而今以此为言。诚莫知其意也。)且此十六字。乃开卷第一义。而其义之不明于世久矣。吕温胡广之中庸。皆出于不识此义。而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者。亦未足以尽其义。故特以此加之于篇首而著之于二章。又编之于通解。其丁宁反复为天下后世虑也深且切矣。今以为不必复出而一笔削去。此果知朱子之意而尊信严畏者耶。(孝经闺门章。不过二十二字。而司马贞削去之。识者以为卒启开元无礼之祸。圣贤之言。其可容易删减乎。)且大学篇题中。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十五字。及中庸篇题中恐其久而差也六字之删去。又何意也。岂差之一字。切中其忌讳。故不欲言之。如蔡京之讳言危亡乱字耶。朱夫子定著章句。自谓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3H 页
 一生精力。尽在此书。又曰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量轻重。方敢写出。此果一字可以复减。一字可以复增者耶。后之学者。所当信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虽夫子平日之言。苟在集注章句之外者。固不当辄自添入。以乱其洁净精微之体。况敢曰剟取要旨。而肆然羼录于成书之中耶。(中庸篇题十六字。考之唐本。或有与程子说连书者。其意亦可见矣。)
一生精力。尽在此书。又曰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量轻重。方敢写出。此果一字可以复减。一字可以复增者耶。后之学者。所当信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虽夫子平日之言。苟在集注章句之外者。固不当辄自添入。以乱其洁净精微之体。况敢曰剟取要旨。而肆然羼录于成书之中耶。(中庸篇题十六字。考之唐本。或有与程子说连书者。其意亦可见矣。)册子曰二篇篇题下端。所添所删。实仿通解篇题。而或谓之代以己说。或谓之代以他说。夫己说云者。别立己见之谓也。他说云者。旁取他人言论之谓也。今大学篇题之末。谨书之曰旧本多错简云云。此则推本通解篇题之意。以志朱子绪正之事。果有一言一字别立己见者乎。中庸篇题之末。谨书之曰朱子曰闻之先君子云云。此则谨取通解篇题之语。以志朱子过庭之训。果有一分近似于旁取他人之言论乎。
辨曰既自谓剟取推本则非己说而何。既非章句之文则非他说而何。今类编之罪。正在于纷改经传。而尚以剟取推本之说。张皇文饰。曾谓世人俱无眼目而可欺乎。况经义之得失。系于一字一句之间去取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3L 页
 裁量。非权度之精切者。不可为也。今乃以剟取要旨。推本遗意自居。不亦颠哉。(圣人能知圣人。锡鼎既无见识。则何以知遗意与要旨哉。)
裁量。非权度之精切者。不可为也。今乃以剟取要旨。推本遗意自居。不亦颠哉。(圣人能知圣人。锡鼎既无见识。则何以知遗意与要旨哉。)册子曰子程子之上子字。删而不书者。庸学既列于礼经。则曲礼以下诸篇所引程朱说。皆称程子朱子而不加上子字。通解首卷二书篇题。只称程氏而不称子程子。故谨依此例。以从一格。以本篇言之。首段之外。只称程子。论孟诸书。并皆称程子。
辨曰子程子之上子字。朱夫子岂无深意而剩加之哉。如论孟诸书集注。皆只称程子。而独于庸学篇题复加一子字者。以庸学乃传道之书。而程子之所表章。故特加之以示尊师之意。若以章句中只称程子而欲从一格。则中庸序中初头则称子思子。而其下并只称子思。亦当删去下子字。以从一格欤。且通解中庸篇题。明称以子程子。则此所谓只称程氏者。亦何据也。今此类编。礼记集注则用陈氏。庸学章句则用朱子。其体自相不同。而乃以浅狭之见。随手点窜。以作一格。则穿凿破坏。势所必至。而犹且不肯自服其僭妄。尚何言哉。(礼记集注之纷乱。不止于庸学章句。而今不暇论。)
册子曰音注八字之删。既非妙道精义之所关。且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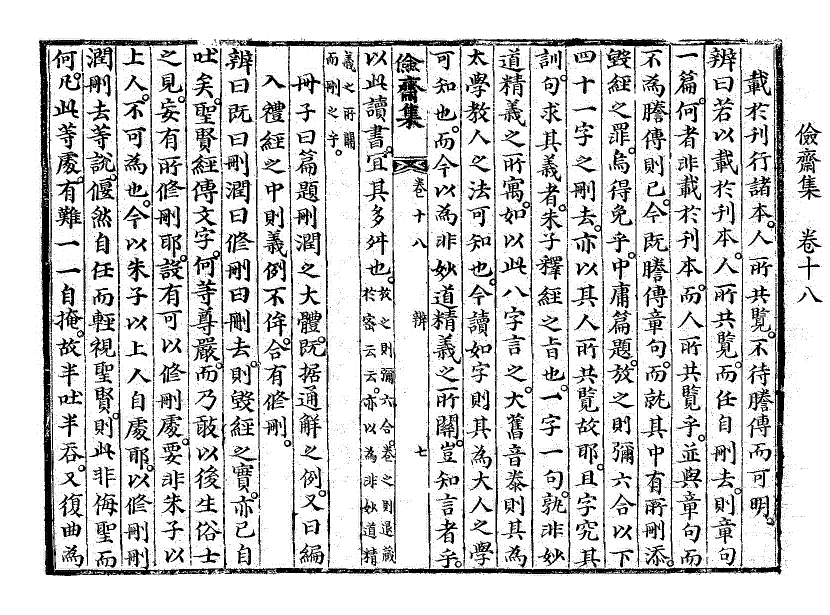 载于刊行诸本。人所共览。不待誊传而可明。
载于刊行诸本。人所共览。不待誊传而可明。辨曰若以载于刊本。人所共览。而任自删去。则章句一篇。何者非载于刊本。而人所共览乎。并与章句而不为誊传则已。今既誊传章句。而就其中有所删添。毁经之罪。乌得免乎。中庸篇题。放之则弥六合以下四十一字之删去。亦以其人所共览故耶。且字究其训。句求其义者。朱子释经之旨也。一字一句。孰非妙道精义之所寓。如以此八字言之。大旧音泰则其为太学教人之法可知也。今读如字则其为大人之学可知也。而今以为非妙道精义之所关。岂知言者乎。以此读书。宜其多舛也。(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云云。亦以为非妙道精义之所关而删之乎。)
册子曰篇题删润之大体。既据通解之例。又曰编入礼经之中则义例不侔。合有修删。
辨曰既曰删润曰修删曰删去。则毁经之实。亦已自吐矣。圣贤经传文字。何等尊严。而乃敢以后生俗士之见。妄有所修删耶。设有可以修删处。要非朱子以上人。不可为也。今以朱子以上人自处耶。以修删删润删去等说。偃然自任而轻视圣贤。则此非侮圣而何。凡此等处。有难一一自掩。故半吐半吞。又复曲为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4L 页
 之说。以眩 天聪。而辄下谨依谨书谨取等谨字。外示恭逊之态。而内售荧惑之计。即此一心。已不足与论于圣贤之训也。
之说。以眩 天聪。而辄下谨依谨书谨取等谨字。外示恭逊之态。而内售荧惑之计。即此一心。已不足与论于圣贤之训也。册子曰先儒勉斋黄干。著通解续篇。其编定凡例。与朱子通解固多有异同处。其祭礼篇引中庸数段。用朱子本注而多所添删。又曰始朱子以丧祭二礼属勉斋修正。其后勉斋谓其门人杨复曰向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礼。其悉用此规模更定之。以此观之。黄氏续编虽不规规于一遵通解。而可谓得朱子之心矣。今不究委折之如斯。直以为背异于朱子。则勉斋岂能心服乎。
辨曰今日若无悉遵通解之言而言者。倘攻其不用通解规模则以此自證可也。今之所攻者。乃纷改章句等成书也。勉斋续编之异同于通解。有何所与而援而自證耶。续篇与通解。自是别书。且其凡例。亦尝奉质于朱子而得其印可。则此是朱子之意也。未知今之纷改经传者。亦曾面禀如勉斋否乎。祭礼篇引中庸章句数段。而有所添删云者。亦非实状也。续编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5H 页
 笺注。乃勉斋之所自纂定也。祭礼篇注中虽用中庸章句之意。而非引用朱子之言也。其文句之不同势也。观其不曰先师文公先生曰则可知也。(续编中凡引用朱子之言。必曰先师文公先生云云。)岂若今日全用章句。且曰朱子章句。而自以己意僭行删添于其间者乎。今以朱子尝许勉斋以吾所编礼。其用此更定之语。而便谓通解不足信。因通解又推及于庸学章句。不欲规规遵信。则将何所不至哉。勉斋亲承师训。而犹不敢轻改于通解。今乃妄意推测而肆行胸臆于他书。不亦痛乎。勉斋岂能心服之说。亦极悖谬无稽矣。
笺注。乃勉斋之所自纂定也。祭礼篇注中虽用中庸章句之意。而非引用朱子之言也。其文句之不同势也。观其不曰先师文公先生曰则可知也。(续编中凡引用朱子之言。必曰先师文公先生云云。)岂若今日全用章句。且曰朱子章句。而自以己意僭行删添于其间者乎。今以朱子尝许勉斋以吾所编礼。其用此更定之语。而便谓通解不足信。因通解又推及于庸学章句。不欲规规遵信。则将何所不至哉。勉斋亲承师训。而犹不敢轻改于通解。今乃妄意推测而肆行胸臆于他书。不亦痛乎。勉斋岂能心服之说。亦极悖谬无稽矣。册子曰释本末章。自两程釐正。已多异同。诸家论说。亦非一二。观于李霈霖所谓人多疑释纲领条目之中。不当释本末为疑云者。亦可见其一端矣。至于先正臣李彦迪则遂移置经文之下。而先正臣李珥之论。亦不曾深斥矣。区区之意。窃尝疑三纲领之后八条目之前。另出本末之传。恐欠十分稳当。且明德新民两传。皆引诗书而各有结语。今此至善之传。五引诗而无一句结语。文体亦欠伦整。妄意听讼犹人固善矣。必也使无讼。乃为至善。经文意趣。亦似有解释至善之义。及见玉溪卢氏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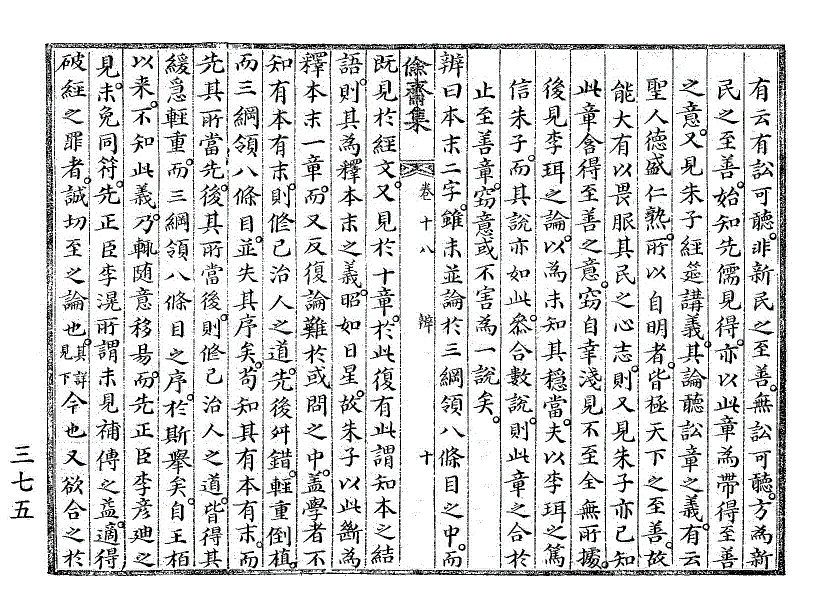 有云有讼可听。非新民之至善。无讼可听。方为新民之至善。始知先儒见得。亦以此章为带得至善之意。又见朱子经筵讲义。其论听讼章之义。有云圣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极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则又见朱子亦已知此章含得至善之意。窃自幸浅见不至全无所据。后见李珥之论。以为未知其稳当。夫以李珥之笃信朱子。而其说亦如此。参合数说。则此章之合于止至善章。窃意或不害为一说矣。
有云有讼可听。非新民之至善。无讼可听。方为新民之至善。始知先儒见得。亦以此章为带得至善之意。又见朱子经筵讲义。其论听讼章之义。有云圣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极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则又见朱子亦已知此章含得至善之意。窃自幸浅见不至全无所据。后见李珥之论。以为未知其稳当。夫以李珥之笃信朱子。而其说亦如此。参合数说。则此章之合于止至善章。窃意或不害为一说矣。辨曰本末二字。虽未并论于三纲领八条目之中。而既见于经文。又见于十章。于此复有此谓知本之结语。则其为释本末之义。昭如日星。故朱子以此断为释本末一章。而又反复论难于或问之中。盖学者不知有本有末。则修己治人之道。先后舛错。轻重倒植。而三纲领八条目。并失其序矣。苟知其有本有末。而先其所当先。后其所当后。则修己治人之道。皆得其缓急轻重。而三纲领八条目之序。于斯举矣。自王柏以来。不知此义。乃辄随意移易。而先正臣李彦迪之见。未免同符。先正臣李滉所谓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者。诚切至之论也。(其详见下。)今也又欲合之于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6H 页
 至善之章。则亦非王李之说也。人人皆欲纷乱如此。朱子成书宁复有完全者。而古圣人作经垂训之意。安得著明于世乎。夫大学中所引诗书。每段多有结语。而止至善章末段引诗。君子亲其亲以下。乃其结语。则何待复加结语然后为伦整哉。况引孔子之语。与引诗引书。其义无异。不足为结语。而此谓知本四字。又非止至善之结语。则必欲以此合之于上章者。果何意耶。大学一篇。言其功效处。何往而非至善乎。故玉溪卢氏之说。朱子讲义之言。虽有至善二字。正所以解释知本之义也。以其有至善字而遽谓之释至善之意。则释新民章。亦有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之文。又将移属此章于至善章欤。且朱子此言。既见于或问中论本末之章。则其意亦已明矣。今不曰或问而曰经筵讲义者。有若朱子别生一义于告君之际。而章句或问为未定之论者然。亦可见其用意之崎岖也。每引李珥之言以自文饰。而李珥何尝曰朱子之说不可遵信。而移属于至善之章乎。其意果如此则何不明言而只示意旨。以待今日之锡鼎乎。大学设是朱子之所自作。固当尊信。同于曾子。而况以朱子而注曾子之书乎。今乃不信其手自定著明
至善之章。则亦非王李之说也。人人皆欲纷乱如此。朱子成书宁复有完全者。而古圣人作经垂训之意。安得著明于世乎。夫大学中所引诗书。每段多有结语。而止至善章末段引诗。君子亲其亲以下。乃其结语。则何待复加结语然后为伦整哉。况引孔子之语。与引诗引书。其义无异。不足为结语。而此谓知本四字。又非止至善之结语。则必欲以此合之于上章者。果何意耶。大学一篇。言其功效处。何往而非至善乎。故玉溪卢氏之说。朱子讲义之言。虽有至善二字。正所以解释知本之义也。以其有至善字而遽谓之释至善之意。则释新民章。亦有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之文。又将移属此章于至善章欤。且朱子此言。既见于或问中论本末之章。则其意亦已明矣。今不曰或问而曰经筵讲义者。有若朱子别生一义于告君之际。而章句或问为未定之论者然。亦可见其用意之崎岖也。每引李珥之言以自文饰。而李珥何尝曰朱子之说不可遵信。而移属于至善之章乎。其意果如此则何不明言而只示意旨。以待今日之锡鼎乎。大学设是朱子之所自作。固当尊信。同于曾子。而况以朱子而注曾子之书乎。今乃不信其手自定著明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6L 页
 白可见之文字。而必欲暗揣冥索于峣崎侧僻之中。而曰遗意如此。意旨可知何也。李霈霖固不知何许人。而其言则盖以辨斥疑者之说。而今反引而自證。亦可谓遁辞知其所穷矣。
白可见之文字。而必欲暗揣冥索于峣崎侧僻之中。而曰遗意如此。意旨可知何也。李霈霖固不知何许人。而其言则盖以辨斥疑者之说。而今反引而自證。亦可谓遁辞知其所穷矣。册子曰大学传之三四章。合为一节者。盖以中庸分节之例。或以单章为节。或并数章为节。故略仿此例。以二章为一章。或问所谓大学分节。与中庸作对云者此也。尚存三章四章之目。不敢不存其本注。此则有不敢辄引删去。亶出于严畏之意。又曰所谓作对云者。言大学分节。既仿中庸之例。其两篇章节之分解。自相符合云尔。如周易上经首乾坤而终于坎离。下经首咸恒而终于未济。先儒云以气化形化。阴阳对待为义。诗经关雎后妃之德而麟趾为关雎之应。鹊巢夫人之德而驺虞为鹊巢之应。此外经义之分配作对。非止一二。
辨曰既移属上章合为一节。而尚存其目存其本注者。果是不敢辄删亶出严畏之意。则其分章之背异。篇题之删添。笺注之汩乱。何无严畏之意而敢于为也。且朱子分章之例。一事为一章。而每章之下。必曰右释某义。而今也第三章下。独无右释某义之文。而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7H 页
 至第四章然后。合并而书之曰右释止于至善云者。已不成义理。第四章章句只释本末之义。无一释至善之意。而今曰释止至善而尚存释本末之章句。观其章句则本末章也。观其章下则释至善章也。其杂乱无统。不亦甚乎。如此而自谓伦整通顺。其谁信之。(锡鼎谓朱子分章。例无两子曰字。而欲改第二十八章则朱子分章。岂有两章释一义之例乎。此则何不用朱子分章之例耶。以此观之。朱子分章之例云云。皆是文饰之说也。)经义之分配作对者。非止一二。所引诗经周易。亦固是矣。而此皆一书之中。以义理自相分对照应者也。何尝以周易对诗经。书经对春秋。又何尝计其章次之多寡。篇简之长短而作对。如今日耶。夫中庸大学。作者非一人。意义非一例。而强而配之曰俾令作对云者。岂不浅近而可笑者乎。(俾令二字尤可笑。)
至第四章然后。合并而书之曰右释止于至善云者。已不成义理。第四章章句只释本末之义。无一释至善之意。而今曰释止至善而尚存释本末之章句。观其章句则本末章也。观其章下则释至善章也。其杂乱无统。不亦甚乎。如此而自谓伦整通顺。其谁信之。(锡鼎谓朱子分章。例无两子曰字。而欲改第二十八章则朱子分章。岂有两章释一义之例乎。此则何不用朱子分章之例耶。以此观之。朱子分章之例云云。皆是文饰之说也。)经义之分配作对者。非止一二。所引诗经周易。亦固是矣。而此皆一书之中。以义理自相分对照应者也。何尝以周易对诗经。书经对春秋。又何尝计其章次之多寡。篇简之长短而作对。如今日耶。夫中庸大学。作者非一人。意义非一例。而强而配之曰俾令作对云者。岂不浅近而可笑者乎。(俾令二字尤可笑。)册子曰此谓知本一句。旧本在本乱末治之下。非新移也。上文既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则此谓知本。窃恐宜为结辞。三纲领之下。以知止承之。八条目之下。以知本结之。可见为学之道。必以知为先。而阳明之知行合一。释氏之戒定生慧。其不合于圣人之学。而自为异说者。又可见矣。盖朱子之训。每以先知后行为主。又曰今以衍文还存于经下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7L 页
 则既合于程训。而实遵朱子心法。
则既合于程训。而实遵朱子心法。辨曰此句程子连听讼章移之于经文之下。而特以此句为衍文。朱子又移置于此。断为第五章。而此句则仍从程子为衍文。此意已具于或问曰复出而他无所系。又曰知属之经后者之不然。其言若是丁宁。而犹且违弃而自立己见则尚何言哉。今乃就程子之说而分此一段。听讼云云则合之于第三章。此句则还置于经后。此乃今日之新割。而亦非程子之旧也。而自谓合于程训则其谁欺乎。且合于程训云者。以为衍文之谓也。实遵朱子心法云者。以知为先之谓也。既为衍文则无义可说矣。既有其义则不当为衍文。古今天下。安有以衍文而释实事之经义乎。况此谓知本之云。乃传文结语之例。而非经文之体也。又与听讼章结语为重叠。而一篇之内。更无此例。则其为衍文。毫无可疑。而今以为经文之结语者。亦陋矣。至于格致之说。既反复于经文。而传则又自为一章。以补其亡。其义至矣尽矣。何待此复着一知字而后为益明哉。拖引阳明佛氏以文其说。全不衬着矣。盖锡鼎于义理。本无实见。而率意强言。惟欲以新巧求多。故其说之偏枯破绽。每每如此矣。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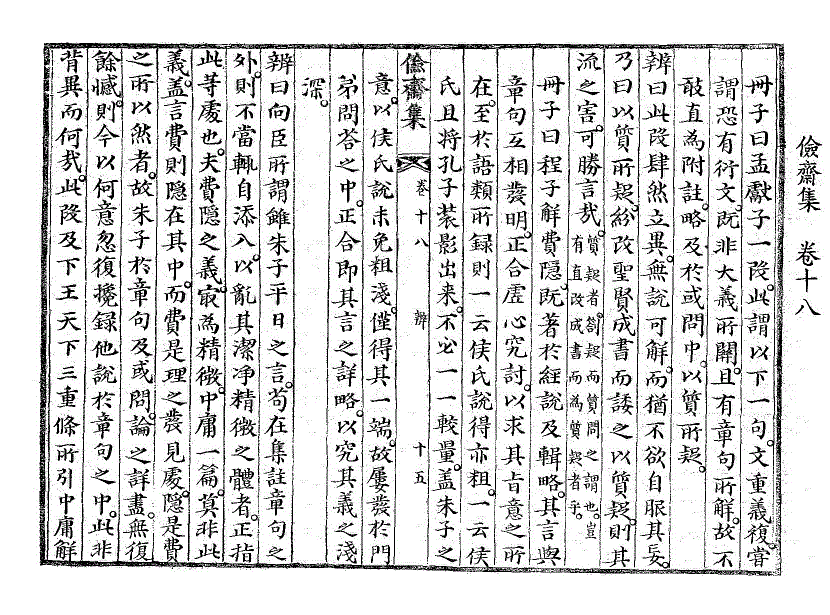 册子曰孟献子一段。此谓以下一句。文重义复。尝谓恐有衍文。既非大义所关。且有章句所解。故不敢直为附注。略及于或问中。以质所疑。
册子曰孟献子一段。此谓以下一句。文重义复。尝谓恐有衍文。既非大义所关。且有章句所解。故不敢直为附注。略及于或问中。以质所疑。辨曰此段肆然立异。无说可解。而犹不欲自服其妄。乃曰以质所疑。纷改圣贤成书而诿之以质疑。则其流之害。可胜言哉。(质疑者。劄疑而质问之谓也。岂有直改成书而为质疑者乎。)
册子曰程子解费隐。既著于经说及辑略。其言与章句互相发明。正合虚心究讨。以求其旨意之所在。至于语类所录则一云侯氏说得亦粗。一云侯氏且将孔子装影出来。不必一一较量。盖朱子之意。以侯氏说未免粗浅。仅得其一端。故屡发于门弟问答之中。正合即其言之详略。以究其义之浅深。
辨曰向臣所谓虽朱子平日之言。苟在集注章句之外。则不当辄自添入。以乱其洁净精微之体者。正指此等处也。夫费隐之义。最为精微。中庸一篇。莫非此义。盖言费则隐在其中。而费是理之发见处。隐是费之所以然者。故朱子于章句及或问。论之详尽。无复馀憾。则今以何意忽复搀录他说于章句之中。此非背异而何哉。此段及下王天下三重条所引中庸解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8L 页
 无德位而作礼乐云云。虽曰程子经说而晁德昭读书志以为明道解。大至集以为伊川解。两说不同。而朱子以为吕氏讲堂改本。而非程子之言也。立说以辨之。其编于二程全书则乃后人所为。而其下亦载朱子之论。至于中庸王天下章句所引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云云。及好学近乎知章句所引愚者自是而不求云云。皆此经说中语。而朱子断作吕氏之说。而今乃以为程子解。则亦不遵朱子之定论矣。(辑略只曰费日用处。经说只曰费用之广也。隐微密也。圣人所不知不能。所谓隐也云云。而今所搀录。亦多以意添删。)朱子又尝曰旧人多将圣人不知不能处做隐。觉得下面都说不去。且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亦何尝隐来。以此观之。朱子之不取此说。已有明證。或问之辨。亦且如彼。而今皆不信。偃然添入于成书之中。且曰似与章句所解有异。以为汩乱正义之计。其下又附语类一条。以示不足于章句之意。其必欲倒戈于朱子。亦已狼藉矣。噫侯氏说。语类固有云云。而然又尝曰圣人亦有一两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问官名学礼之类是已。董铢问以孔子不得位。为圣人所不能。窃谓禄位名寿。此在天者。圣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说大德必得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
无德位而作礼乐云云。虽曰程子经说而晁德昭读书志以为明道解。大至集以为伊川解。两说不同。而朱子以为吕氏讲堂改本。而非程子之言也。立说以辨之。其编于二程全书则乃后人所为。而其下亦载朱子之论。至于中庸王天下章句所引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云云。及好学近乎知章句所引愚者自是而不求云云。皆此经说中语。而朱子断作吕氏之说。而今乃以为程子解。则亦不遵朱子之定论矣。(辑略只曰费日用处。经说只曰费用之广也。隐微密也。圣人所不知不能。所谓隐也云云。而今所搀录。亦多以意添删。)朱子又尝曰旧人多将圣人不知不能处做隐。觉得下面都说不去。且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亦何尝隐来。以此观之。朱子之不取此说。已有明證。或问之辨。亦且如彼。而今皆不信。偃然添入于成书之中。且曰似与章句所解有异。以为汩乱正义之计。其下又附语类一条。以示不足于章句之意。其必欲倒戈于朱子。亦已狼藉矣。噫侯氏说。语类固有云云。而然又尝曰圣人亦有一两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问官名学礼之类是已。董铢问以孔子不得位。为圣人所不能。窃谓禄位名寿。此在天者。圣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说大德必得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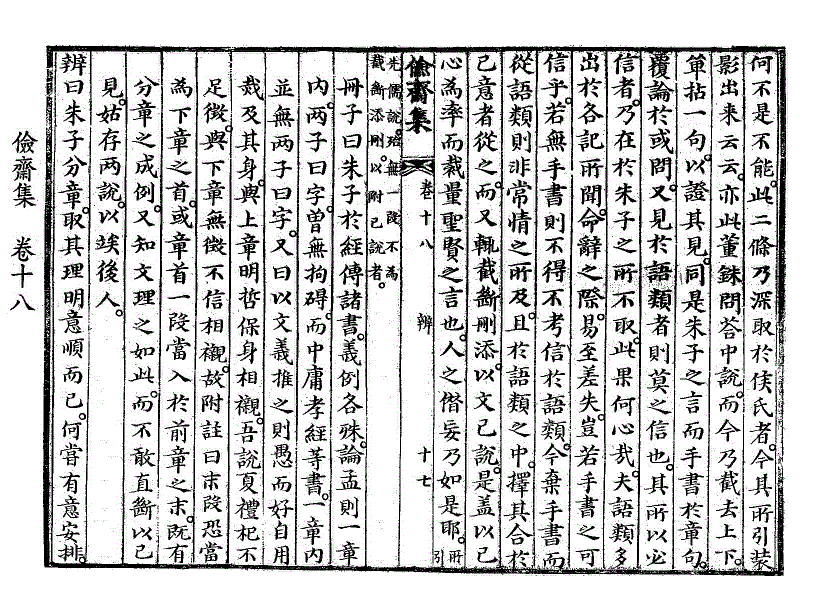 何不是不能。此二条乃深取于侯氏者。今其所引装影出来云云。亦此董铢问答中说。而今乃截去上下。单拈一句。以證其见。同是朱子之言而手书于章句。覆论于或问。又见于语类者则莫之信也。其所以必信者。乃在于朱子之所不取。此果何心哉。夫语类多出于各记所闻。命辞之际。易至差失。岂若手书之可信乎。若无手书则不得不考信于语类。今弃手书而从语类则非常情之所及。且于语类之中。择其合于己意者从之。而又辄截断删添。以文己说。是盖以己心为率而裁量圣贤之言也。人之僭妄乃如是耶。(所引先儒说。殆无一段不为截断添删。以附己说者。)
何不是不能。此二条乃深取于侯氏者。今其所引装影出来云云。亦此董铢问答中说。而今乃截去上下。单拈一句。以證其见。同是朱子之言而手书于章句。覆论于或问。又见于语类者则莫之信也。其所以必信者。乃在于朱子之所不取。此果何心哉。夫语类多出于各记所闻。命辞之际。易至差失。岂若手书之可信乎。若无手书则不得不考信于语类。今弃手书而从语类则非常情之所及。且于语类之中。择其合于己意者从之。而又辄截断删添。以文己说。是盖以己心为率而裁量圣贤之言也。人之僭妄乃如是耶。(所引先儒说。殆无一段不为截断添删。以附己说者。)册子曰朱子于经传诸书。义例各殊。论孟则一章内。两子曰字。曾无拘碍。而中庸孝经等书。一章内并无两子曰字。又曰以文义推之则愚而好自用灾及其身。与上章明哲保身相衬。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与下章无徵不信相衬。故附注曰末段恐当为下章之首。或章首一段当入于前章之末。既有分章之成例。又知文理之如此。而不敢直断以己见。姑存两说。以俟后人。
辨曰朱子分章。取其理明意顺而已。何尝有意安排。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79L 页
 不问义理之如何。只观两子曰之有无乎。此章上有子曰而其下有子思之言。故又以子曰结之。如此处虽有十子曰。亦何害乎。今谓中庸孝经一章内并无两子曰字。而孝经首章上。有子曰字而其下有曾子之对。故又以子曰起之。若以有两子曰而分为两章则不成伦理矣。且朱子之分章也。岂不知此章内有两子曰字乎。而今以朱子分章之例。反攻朱子。一则曰与上章相衬。一则曰与下章相衬。一则曰文理如此。直归章句于文理不顺。上下不衬之科。尊信严畏者固若是乎。(若引他书例。以攻朱子则犹之可也。今乃以朱子分章之例。反攻朱子之分章。果成说乎。)
不问义理之如何。只观两子曰之有无乎。此章上有子曰而其下有子思之言。故又以子曰结之。如此处虽有十子曰。亦何害乎。今谓中庸孝经一章内并无两子曰字。而孝经首章上。有子曰字而其下有曾子之对。故又以子曰起之。若以有两子曰而分为两章则不成伦理矣。且朱子之分章也。岂不知此章内有两子曰字乎。而今以朱子分章之例。反攻朱子。一则曰与上章相衬。一则曰与下章相衬。一则曰文理如此。直归章句于文理不顺。上下不衬之科。尊信严畏者固若是乎。(若引他书例。以攻朱子则犹之可也。今乃以朱子分章之例。反攻朱子之分章。果成说乎。)册子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文理终欠通畅。先儒诸家。固多疑之。三重一句。若在于上章非天子不议礼之上则文从字顺。辞义允当。程子中庸解曰无德位而作礼乐。居周世而从夏殷。取灾之道也。故王天下有三重焉云云。夫三重一句。本在下章之首。而乃以此句入于议礼之上而通作注说。程子之意固已较然。吕氏注亦曰三重议礼制度考文。其意亦自分晓。附注以为前章之脱简者。盖本于此。夫然则寡过一句。自当直承吾从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0H 页
 周之下。文理亦甚衬贴。盖子曰今用之吾从周云者。言周礼未必尽善。而此乃时王之制。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故解云从时王而寡过。敢于吕注之下。略有附论耳。
周之下。文理亦甚衬贴。盖子曰今用之吾从周云者。言周礼未必尽善。而此乃时王之制。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故解云从时王而寡过。敢于吕注之下。略有附论耳。辨曰朱子尝曰此章明白无可商量。但三重说者多耳。故三重之义则特取吕氏之说以编于章句。而今乃曰文理终欠通畅。与朱子此章明白之说。一何相反欤。又以三重说者多。故因此囫囵为说曰先儒诸家固多疑之。有若并一章尽疑之。而己见有所承受者然。不亦太妆撰乎。(非但此章。其于卞解之际。妆撰文饰。大抵皆此类。)所引程解之为吕说则前既辨之。而章句所引三重云云。即此段之文也。考其全文。何尝曰移属于非天子不议礼之上乎。今乃曰其意亦自分晓。果何据耶。(凡曰分晓曰较然。下语极巧。)且此经说。非吕氏之说则是程子之说也。是程子之说则非吕氏之说也。二者必居一于此。而今乃分此一段。或以为程子。或以为吕氏。欲以广作證援。眩惑耳目。在他人尚不可。况于告君之辞乎。至于周礼未必尽善而此乃时王之制。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故解曰从时王而寡过云云者。其意盖以为周礼未尽善。当在议作之科。而特以其不尊。故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0L 页
 不得不从周则仅得寡过云尔。此所以裂移寡过一句于从周之下。而自谓独得妙悟文理衬贴者也。此条最为害理。非特文义之误解而已。何者。昔张九成之见正如此。解此句曰周法已弊。其过多矣。孔子身非辅相。不在尊位。所以不敢轻议妄论而曲意以从周之法度也。朱子驳之曰孔子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其从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从之也。其不得不从者。是亦义理所在。而以为曲意而从。非圣人之心也。张氏归心释氏而曲意于儒者。故其所以窥圣人者如此。今玆所谓周礼未必尽善者。即周法已弊。其过多者也。所谓从时王之寡过者。即不在尊位。不敢轻议。曲意从周者也。此未必自相循袭。而只以偏曲之见。妄揣经旨。故其误认错解如出一手。而朱子之驳论。又先正其心术。辞严义峻。似若为今日准备。讵不幸欤。其自信分晓。至欲纷改正经者。犹且如此。则其他可以类推而有不足辨者矣。
不得不从周则仅得寡过云尔。此所以裂移寡过一句于从周之下。而自谓独得妙悟文理衬贴者也。此条最为害理。非特文义之误解而已。何者。昔张九成之见正如此。解此句曰周法已弊。其过多矣。孔子身非辅相。不在尊位。所以不敢轻议妄论而曲意以从周之法度也。朱子驳之曰孔子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其从周也亦有道矣。非不得已而妄从之也。其不得不从者。是亦义理所在。而以为曲意而从。非圣人之心也。张氏归心释氏而曲意于儒者。故其所以窥圣人者如此。今玆所谓周礼未必尽善者。即周法已弊。其过多者也。所谓从时王之寡过者。即不在尊位。不敢轻议。曲意从周者也。此未必自相循袭。而只以偏曲之见。妄揣经旨。故其误认错解如出一手。而朱子之驳论。又先正其心术。辞严义峻。似若为今日准备。讵不幸欤。其自信分晓。至欲纷改正经者。犹且如此。则其他可以类推而有不足辨者矣。册子曰先儒于经传正文。直为移换处。不一而足。又曰陈浩于礼经正文。王制之大夫祭器不假。坊记之民犹自献其身。乐记之末节数段。或移章段。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1H 页
 或割句字。又曰就洛诰论之。固未尝移动。只注其下。而设若以鈲裂移动之罪。加之为蔡氏者。不亦冤乎。又曰思卞录则曰寡过矣上。当有阙文云。此与类编所论不啻径庭。而今谓之遵袭。不亦谬乎。
或割句字。又曰就洛诰论之。固未尝移动。只注其下。而设若以鈲裂移动之罪。加之为蔡氏者。不亦冤乎。又曰思卞录则曰寡过矣上。当有阙文云。此与类编所论不啻径庭。而今谓之遵袭。不亦谬乎。辨曰今之言者。何尝曰错简不可正。误字不可改乎。特以其已经朱子之手。理明义精。如日中天。则不可以躁妄之见。敢有毁凿于成书之中也。东汇九峰亦尝有毁凿朱子所定之经传者乎。广引其不当引以自比援。是其意以朱子之成书。为尚多可议。而未及是正而已得以正之也。其立心如此。宜其有今日也。思卞录固多背违于朱子者。而然不过劄记之私书也。岂若今日直改成书。坏弄无忌乎。而乃不欲比伦则亦可谓明于人而暗于己也。蔡氏亦冤之云。与上勉斋岂能心服。同一语意。今不再辨。
册子曰孝经之编入戴记。亦有说焉。盖孝经是孔曾论孝之言。最为紧切。既列于十三经则宜入于五经之内。而且与戴记中燕居闲居等篇。文体恰相伦类。理致允为衬贴。且礼记孝经当为附合。亦有朱子之说。编入于学礼盖为是也。至于刊误所定。盖是一时草定之本。朱子盖欲仿大学之例。分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1L 页
 为经传。又尝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孝经之旨者。别为外传而书未成。要为未定之论。若果以此为定本则宜有以上下移易。一从刊误所定。写出成书如大学武成之为。而今乃不然。经文无一变动。只录分章草本。则其非为定论。此亦可知。窃想当时草藁藏在箧笥。大全编辑时。门弟子不敢不录。收入于杂著耳。夫圣作谓之经。贤述谓之传云云。又曰大学章句则以孔圣之言为经。曾子之言为传。体段固为得之。文势亦为伦正矣。孝经则不然。首章既有孔曾问答。而其下诸章。亦皆有孔曾问答。此何可分为经传乎。朱子虽分章次。而第九章下题云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当为传之首章。而其论至德。语意亦疏。第八章下题云此一节。释要道。当为传之二章。但经所谓要道自己而推之。与此不同。第二章下题云此一节盖释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三章而文势不通贯。条目不完备。第三章下题云此一节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宜为传之四章。其言虽善而亦非经文之正意。第四章下题云此一节释孝德之本。宜为传之五章。但严父配天。乃赞美之词。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
为经传。又尝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孝经之旨者。别为外传而书未成。要为未定之论。若果以此为定本则宜有以上下移易。一从刊误所定。写出成书如大学武成之为。而今乃不然。经文无一变动。只录分章草本。则其非为定论。此亦可知。窃想当时草藁藏在箧笥。大全编辑时。门弟子不敢不录。收入于杂著耳。夫圣作谓之经。贤述谓之传云云。又曰大学章句则以孔圣之言为经。曾子之言为传。体段固为得之。文势亦为伦正矣。孝经则不然。首章既有孔曾问答。而其下诸章。亦皆有孔曾问答。此何可分为经传乎。朱子虽分章次。而第九章下题云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当为传之首章。而其论至德。语意亦疏。第八章下题云此一节。释要道。当为传之二章。但经所谓要道自己而推之。与此不同。第二章下题云此一节盖释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三章而文势不通贯。条目不完备。第三章下题云此一节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宜为传之四章。其言虽善而亦非经文之正意。第四章下题云此一节释孝德之本。宜为传之五章。但严父配天。乃赞美之词。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2H 页
 也。况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非所以为天下之通训云云。今就此数节而论之。则孝经之难于分为经传。朱子固已自知。而古经文理。亦自明备。类编中遵用古经章次者。实亦探本乎朱子之意。
也。况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非所以为天下之通训云云。今就此数节而论之。则孝经之难于分为经传。朱子固已自知。而古经文理。亦自明备。类编中遵用古经章次者。实亦探本乎朱子之意。辨曰孝经一书。朱子尝疑只前面一段。是当时所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故刊误以本文为经。后人所添补者为传。虽若与大学孔子之言为经。曾子所述为传者。体例不同。然不可以后人所添者。并列于本经。则一为经一为传者。事理之当然也。(大学传中亦有孔子之言。亦可据矣。)朱子之处此。夫岂无义而为之哉。然而每曰孝经难说。故刊误中辄着一疑字。以示慎重之意。以朱子之圣焉而犹不敢专辄如此。况以后生俗子而妄有所论定哉。刊误乃朱子五十七岁时所为也。心与理一。言而世为天下则。则其所定著。宁有毫发馀憾哉。门人书之行状。著于年谱。编于大全。而深山董氏之作大义也。亦一依刊误。则其为定本有何可疑。而今乃遽以为未定之草本。不亦诞妄之甚乎。朱子于传之每章之下。各设疑卞者。非疑其难分经传也。特以其后人所补而文义未莹也。果以为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2L 页
 难分经传则何苦为之刊误乎。其所谓语意亦疏。文势不通云云者。若不分经传则语意密而文势通耶。朱子此言。自不干经传之分不分。而今乃逐条抄录。单行句语。一反其意曰难于分为经传。朱子固已自知。又曰窃想当时草本藏在箧笥。呜呼。此非诬朱子而何。窃想二字。何足以服人心乎。其不信大全行状年谱大义诸书。而妄意揣度于千载之下。必以为未定之草本而扫去不用者。果何心哉。又以不曾上下移易。写出成书。为未定之證。噫是何言乎。今以大全所载观之。果有一毫近似于未定之论乎。况董氏已一遵刊误而成书注解乎。其书俱存。一览可见。而尚腾口舌。左右闪侧。务以御人。益启纷纷。此何事也。今以类编考之。亦不纯用古文。并取古文及刊误以杂就之。而乃自谓遵用古文章次则又非实状也。以孝经附礼记。在锡鼎诚为细故。而言者特言其违弃朱子之训耳。其曰何可以经传分也。曰不可强而分之者。详其语脉。果是逊顺严畏底意耶。(朱子尝言聚论孟礼记言孝处。附之于后。若如今日之言。则孝经亦可附于论孟耶。)难以为说则每称之以质疑。夫肆然立帜。直改成书。是岂质疑之道耶。(刊误与考异不同。而其所作或问则曰大全所载考异。似出于一时编次而非定本也。今则以刊误为未定之草本。何其
难分经传则何苦为之刊误乎。其所谓语意亦疏。文势不通云云者。若不分经传则语意密而文势通耶。朱子此言。自不干经传之分不分。而今乃逐条抄录。单行句语。一反其意曰难于分为经传。朱子固已自知。又曰窃想当时草本藏在箧笥。呜呼。此非诬朱子而何。窃想二字。何足以服人心乎。其不信大全行状年谱大义诸书。而妄意揣度于千载之下。必以为未定之草本而扫去不用者。果何心哉。又以不曾上下移易。写出成书。为未定之證。噫是何言乎。今以大全所载观之。果有一毫近似于未定之论乎。况董氏已一遵刊误而成书注解乎。其书俱存。一览可见。而尚腾口舌。左右闪侧。务以御人。益启纷纷。此何事也。今以类编考之。亦不纯用古文。并取古文及刊误以杂就之。而乃自谓遵用古文章次则又非实状也。以孝经附礼记。在锡鼎诚为细故。而言者特言其违弃朱子之训耳。其曰何可以经传分也。曰不可强而分之者。详其语脉。果是逊顺严畏底意耶。(朱子尝言聚论孟礼记言孝处。附之于后。若如今日之言。则孝经亦可附于论孟耶。)难以为说则每称之以质疑。夫肆然立帜。直改成书。是岂质疑之道耶。(刊误与考异不同。而其所作或问则曰大全所载考异。似出于一时编次而非定本也。今则以刊误为未定之草本。何其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3H 页
 言之自相衡决也。)且以朱子尝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孝经之旨者。别为外传而书未成。为刊误未定之證。此又不成说之言也。刊误自刊误。外传自外传。何可以外传之未及就勒。断刊误之未定乎。朱子尝欲取古今女范作为一书。以配小学。篇目已定而亦未及成。若如锡鼎之说则小学亦为未定之书耶。(按刊误跋文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观此其不为外传。不敢之意。而非未及成也。)家礼明是朱子未及修正之书。而金就砺尝请李滉考證裁量。以成一部礼书。滉非之曰古所谓大礼。与天地同其序。既未窥其本原。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未知其节文。而乃相与出位犯分。率意妄作增损乎。大贤之成书。其能无专僭之谤而免于罪戾乎。以李滉而尚不敢。则况于俗士乎。以家礼而尚不可则况于刊误乎。
言之自相衡决也。)且以朱子尝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孝经之旨者。别为外传而书未成。为刊误未定之證。此又不成说之言也。刊误自刊误。外传自外传。何可以外传之未及就勒。断刊误之未定乎。朱子尝欲取古今女范作为一书。以配小学。篇目已定而亦未及成。若如锡鼎之说则小学亦为未定之书耶。(按刊误跋文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观此其不为外传。不敢之意。而非未及成也。)家礼明是朱子未及修正之书。而金就砺尝请李滉考證裁量。以成一部礼书。滉非之曰古所谓大礼。与天地同其序。既未窥其本原。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未知其节文。而乃相与出位犯分。率意妄作增损乎。大贤之成书。其能无专僭之谤而免于罪戾乎。以李滉而尚不敢。则况于俗士乎。以家礼而尚不可则况于刊误乎。册子曰泮疏且引或问所谓求之于文字而章句顺比。考之于义理而节文妥适。其不合于圣贤本旨者几希。其间尽有自信其必然。俟百世而不惑等语而斥之以凌驾前贤。妄自尊大。噫是何言耶。或问云云。即末端总结之辞。而皆取戴记诸篇言之。其于庸学绝无相干。又曰臣于戴记。潜心研究。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3L 页
 积数十年。篇章之合分。训解之得失。往往有看得分明处。乃于或问总论之际。窃不自逊。敢有所道。又曰观于节文妥适之云。可知其为论说礼经之辞。庸学二篇。何尝有节文之可论者耶。
积数十年。篇章之合分。训解之得失。往往有看得分明处。乃于或问总论之际。窃不自逊。敢有所道。又曰观于节文妥适之云。可知其为论说礼经之辞。庸学二篇。何尝有节文之可论者耶。辨曰其所谓或问者。既总论一书。而妄自夸诩。则观者安知其意独不在于庸学乎。既以节文二字。归之于礼经。则章句二字将何归耶。礼经亦有章句之称耶。且礼经亦多编入通解。曾经朱子之论定者。而今其分门析义。并与之违异。零分琐缀。务求奇巧。而穿凿破碎。不成伦理处。亦多有之。乃自谓潜心研究积数十年。往往有看得分明处云。何必数十年。设令穷一生之力。只研究得背异朱子处。则可谓枉用其心矣。虽然朱子尝谓王氏新经尽有好处。今亦岂无一二看得好处。但以其便儇佼厉之习。区区掇拾于残篇断简之中。夺此与彼。移东补西。而自谓真得经旨则陋矣。
册子曰且其疏逐节卞论之下。辄云尊信朱子而悉遵义例者。果如是乎。此据序文中句语。以为诘责之辞。而序文所云。盖非论庸学也。特论礼经类分之宏纲大体。皆仿通解尔。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4H 页
 辨曰庸学既在类编之中。而序中总论。初无所分别。则观者何以知其挑出庸学而不为并论乎。虽以此自言者观之。既曰悉遵义例之说。独指礼经而非论庸学。则庸学之不遵朱子。亦已自知而不得掩矣。
辨曰庸学既在类编之中。而序中总论。初无所分别。则观者何以知其挑出庸学而不为并论乎。虽以此自言者观之。既曰悉遵义例之说。独指礼经而非论庸学。则庸学之不遵朱子。亦已自知而不得掩矣。册子曰凡古人有所编述。必为列书讲讨校證诸人。而门生子弟之执役者。并皆参录。以明师友相与之义。且志积年同事之劳。试取唐本书册中验之。其列录师友十居七八。不惟经籍为然。如史编韵书诗选文抄等书。亦多有之。东方刊行书本。监考官及刻手。或多列名附载。既有已事。非今创例。且所云讲确参證。或以面论。或以书问。或以册子付签相难。或因人质问而相确。又非逐段一一质论。亦非诸条并皆印可。往复论难之际。其所印可处亦多。此皆就礼经言之。至于庸学则章段既无擅移。训解亦有章句。虽有一二浅见之所论。顾何事于讲讨论确耶。
辨曰讲确参證之列书三十许人。不过出于浮夸之意。固有不足论者。而第书册中列书姓名。初起于永乐间。承 命纂缉之日。此则事体之所不得已。而其后私书列书一二子弟知旧。则季世之末习也。然亦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4L 页
 实有其事故也。岂若今日以一二段之问答。或许或否。或因人泛问而遽加以讲證之名而张皇列录于书末。至于三十人之多哉。若不并指庸学则何不下一转语。而滥引诬援。同入于侮贤毁经之科也。且讲讨论确之道。岂必待有擅移无章句而后为之耶。抑亦自信其必然。故不须讲讨论确耶。今欲以此求多于前人。而其所取法。乃在于诗选文抄之末习。亦云陋矣。
实有其事故也。岂若今日以一二段之问答。或许或否。或因人泛问而遽加以讲證之名而张皇列录于书末。至于三十人之多哉。若不并指庸学则何不下一转语。而滥引诬援。同入于侮贤毁经之科也。且讲讨论确之道。岂必待有擅移无章句而后为之耶。抑亦自信其必然。故不须讲讨论确耶。今欲以此求多于前人。而其所取法。乃在于诗选文抄之末习。亦云陋矣。册子曰先正臣朴世采居在坡山。臣于忝守海邑时。路过溪寓。为示草本。讲确颇详。其后复以书尺问难。则答书有云类编一书。编次甚善。又以小册子投示于臣。论大学补亡章附注及礼书一段。书册俱在。
辨曰此所谓礼书。似指曾子问中过时不举之义。而前后往复虽多。岂可以此单举而禀问者。遽谓之讲确于类编乎。况末后一书。明辨其误解。而今此附注亦不用先正之言矣。世采尝与林泳书曰闻汝和送渠所纂礼书于令许。末端以季肯兄及生闵彦晖为證。(汝和锡鼎字。季肯朴世堂字。彦晖闵以升字。)此书曾于延城时。略见面目。不省其中勘定当否如何。而其说至此可叹云云。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5H 页
 观此书则过溪寓讲学颇详之说。有不待辨而明者。其有明證者如此。则其他书尺册子亦可知矣。且锡鼎于先贤之说。务立异见。非一日之积。故又尝疑勉斋于续编。大纲虽正而于注疏未暇尽整。恐未可以载于通解。为不可一毫违越。世采诫之曰勉斋亲承朱子之旨。著为成书。周遍齐整。间虽不能尽善。其将直以己见为是而断然不行乎。抑将姑从先儒已定之说而行之乎。此可一言而决矣。其后又诫之曰至以通解续视若未成之书。不欲遵行则恐非小病。其谆谆善诱。随病砭药。出于诚恳者至于此切。而终不悛改。及至今日。又引以自證其书。独不有泚于其颡乎。
观此书则过溪寓讲学颇详之说。有不待辨而明者。其有明證者如此。则其他书尺册子亦可知矣。且锡鼎于先贤之说。务立异见。非一日之积。故又尝疑勉斋于续编。大纲虽正而于注疏未暇尽整。恐未可以载于通解。为不可一毫违越。世采诫之曰勉斋亲承朱子之旨。著为成书。周遍齐整。间虽不能尽善。其将直以己见为是而断然不行乎。抑将姑从先儒已定之说而行之乎。此可一言而决矣。其后又诫之曰至以通解续视若未成之书。不欲遵行则恐非小病。其谆谆善诱。随病砭药。出于诚恳者至于此切。而终不悛改。及至今日。又引以自證其书。独不有泚于其颡乎。册子曰通解一书。规模甚大。至于类编则只取礼经本文。纂次而已。家乡王朝礼之篇目。虽欲尽用通解。其势固不可得矣。又曰类编则只取礼记本经。从文理纂次。此其事理虽欲一遵通解章次。其可得乎。又曰一书中诸篇第次。一篇中各段名目。依仿通解规摹而已。序文中悉仿通解之云。盖谓此也。又曰其汇分就编之际。未尝不取裁于朱子本旨。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5L 页
 辨曰通解与类编体段不同之说是矣。既知其不同则自以为悉仿通解者。又何据而发耶。且已经朱子勘定者。分章析义。多不遵信。此亦出于体段之不同欤。今其缕缕自解者。无非通解不可悉仿之意。而犹以依仿规摹。取裁朱子等说为掩前文过之资。不顾首尾之矛盾。惟欲瞒过于 圣聪何也。(言者若攻其纷改章句则曰悉遵通解义例。言者又发不遵通解之状则曰虽欲尽用通解。其势不可得。其为言可谓惟意所欲矣。)
辨曰通解与类编体段不同之说是矣。既知其不同则自以为悉仿通解者。又何据而发耶。且已经朱子勘定者。分章析义。多不遵信。此亦出于体段之不同欤。今其缕缕自解者。无非通解不可悉仿之意。而犹以依仿规摹。取裁朱子等说为掩前文过之资。不顾首尾之矛盾。惟欲瞒过于 圣聪何也。(言者若攻其纷改章句则曰悉遵通解义例。言者又发不遵通解之状则曰虽欲尽用通解。其势不可得。其为言可谓惟意所欲矣。)册子曰镌(一作鑴)之所著中庸说则以一篇分为十章二十八节。而类编则三十三章固自若也。只就饶氏六节演为九节。又曰与镌(一作鑴)说不啻悬殊。节节相反。而今谓之遵贼镌(一作鑴)而诬朱子何也。
辨曰擅改朱子之成书。同一心法。则小小不同。有不必较挈。而窃详儒疏。亦谓其意欲突过朱子上头者。为不免贼镌(一作鑴)之馀套也。非谓分章分节。一一遵袭也。
册子曰深衣之制。见于朱子家礼。而此书中年草定之后。为一童子所窃去。朱子易箦。其书始出。此非晚年定论可知也。且家礼注蔡氏渊曰司马公书仪所载方领及续衽之制。引證虽详。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尝以理玩经文与身服之宜而得其说。方领之说。已修之家礼。而续衽钩边则未及修耳。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6H 页
 杨氏复曰先生晚年所服深衣。去家礼曲裾之制而不用。盖有深意。及得蔡氏所闻。始知先师所以去旧说不用之意。复取礼记深衣篇熟读之。始知郑注续衽二字。文义甚明。特疏家乱之耳。观此二条则后学之去就从违。亦可推知也。又曰朱子曰近来深衣之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云云。家礼所载。非三代遗制。乃宋时俗㨾。而因用温公书仪。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所忧叹。则又何可胶守而不知变乎。
杨氏复曰先生晚年所服深衣。去家礼曲裾之制而不用。盖有深意。及得蔡氏所闻。始知先师所以去旧说不用之意。复取礼记深衣篇熟读之。始知郑注续衽二字。文义甚明。特疏家乱之耳。观此二条则后学之去就从违。亦可推知也。又曰朱子曰近来深衣之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云云。家礼所载。非三代遗制。乃宋时俗㨾。而因用温公书仪。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所忧叹。则又何可胶守而不知变乎。辨曰朱子论深衣之说。不但见于家礼而已。今此重言复语缕缕引援者。皆是朱子说不可从之意。而至其所自为则剽窃古今诸说而断以己意。凑合而成之也。深衣是三代遗制。而于今可据者。深衣篇及玉藻也。朱子之所讲究者在此。而今乃断以己意于千载之下。则能免妄作之诮乎。据家礼朱子曰去古益远。其冠服制度。仅存可见者。独有此耳。然远方士子亦所罕见。往往人自为制。诡异不经。近于服妖。甚可叹也。此言远方士子不见古制。而妄自为之。如今类编之说。则近于服妖。而今乃截去上下文字。远方士子。改以近来人。自为制。改以深衣之制。而曰家礼所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6L 页
 载本非三代遗制。乃宋时俗㨾。而因用温公书仪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所忧叹云云。此则直以家礼所载。归之于服妖也。顷者姜锡朋等疏。虽未登彻。固已呈院而传播矣。其中有论深衣处。引先师服妖之斥。故今以家礼归之服妖以相对也。锡朋等据家礼而斥渠以服妖。渠则又据己说而斥家礼以服妖。是则慢侮之不足而继之以丑辱也。呜呼尚忍言哉。(锡朋等疏曰深衣制度。无复大全家礼之法。亦尝被先师之所斥。目之以服妖云云。)
载本非三代遗制。乃宋时俗㨾。而因用温公书仪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所忧叹云云。此则直以家礼所载。归之于服妖也。顷者姜锡朋等疏。虽未登彻。固已呈院而传播矣。其中有论深衣处。引先师服妖之斥。故今以家礼归之服妖以相对也。锡朋等据家礼而斥渠以服妖。渠则又据己说而斥家礼以服妖。是则慢侮之不足而继之以丑辱也。呜呼尚忍言哉。(锡朋等疏曰深衣制度。无复大全家礼之法。亦尝被先师之所斥。目之以服妖云云。)册子曰二书本自礼记中挑出。列于四书。依通解还编。实遵朱子之旨。
辨曰儒疏之意。以为还编二书于礼类者。其意正欲因此纷改。以著背异之说。而非如朱子编入仪礼云耳。今乃言东答西。有若魏徵昭陵之对也。
册子曰句语赘剩。承接锄铻。乃据孝经本文中章改舛误而言。非指刊误也。
辨曰亲生之膝下一段。朱子反复疑难。或欲依古文附上章。或欲自为一章。而今乃不用古文。不用朱子。自以己意。移入于下章之末。而曰赘剩曰锄铻。则刊误亦在其中。此非侵逼朱子而何哉。
册子曰戴记一书。句字缺脱。章段错互。繁芜杂乱。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7H 页
 殆不可读。须有一番釐正。乃可为成书。故朱子曰礼记杂乱残阙。或曰经文不可轻改。朱子答曰郑康成解云礼记不合改。如当改处若不改。成甚义理。又答叶贺孙曰间欲将周礼逐项作一揔脑。却以礼记类附。某衰老未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勉力釐正。得成此书。又答胡泳曰编礼不可中辍。今以半日看义理文字。以半日类编礼书。亦不妨。以此观之。编正戴记。即朱子平生雅志也。又曰既欲类附整理。则派分移属。理势之所必至。朱子所云若不改成甚义理。正谓此也。
殆不可读。须有一番釐正。乃可为成书。故朱子曰礼记杂乱残阙。或曰经文不可轻改。朱子答曰郑康成解云礼记不合改。如当改处若不改。成甚义理。又答叶贺孙曰间欲将周礼逐项作一揔脑。却以礼记类附。某衰老未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勉力釐正。得成此书。又答胡泳曰编礼不可中辍。今以半日看义理文字。以半日类编礼书。亦不妨。以此观之。编正戴记。即朱子平生雅志也。又曰既欲类附整理。则派分移属。理势之所必至。朱子所云若不改成甚义理。正谓此也。辨曰礼记虽多脱误。决非小眼目小识见所敢釐正。上文所引李滉之论可见也。况礼记是戴氏集诸家而成之者也。篇篇各为一书。虽有错简。自当求之于本篇之内。如大学错简。未尝取之于中庸是也。今乃零拾琐掇于各篇之中曰。此是某篇之错简。此是某篇之误字。或移其数三字。或割其一二句。殆无一书一章之完全者。可谓礼记之大厄会矣。若以此随手类抄。以资一时之翻阅则或可矣。今欲以为不刊之大典。愚且妄矣。朱子答叶胡之言。各有所指。何与于今日类编之割裂者乎。无朱子之睿圣。无朱子之权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7L 页
 度。而妄自纷乱古经而曰。此朱子平生雅志。则岂非诬朱子之甚者乎。(与叶书是指通解。胡居丧时。尝编次丧礼。自始死以至终丧。各立门目。以呈先生。临归教以云云。此则如今丧礼备要之类。与今类编。天壤不侔。)自言悉遵通解义例。而实则全然相反。今不暇一一辨论。而姑举其大者。天子诸侯之礼。决不可相杂。以乱名分。故通解则王朝礼邦国礼。固自各立门户。而今乃合为一套。以致等威无章之弊。(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今编礼尚不识名分之严。而自谓成朱子之雅志。不亦汰哉。)通解中入于学礼者。类编则入于家礼。通解中属于家礼者。类编则别立嘉礼。如此类不胜其夥。然至于所引朱子语考之。本文或问经文不可轻改曰。改经文。固启学者不敬之心。然旧有一人专攻郑康成解礼记。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时术之亦不改。只作蚕蛾子云。如蚕种之生。循环不息。是何义也。且如大学举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义理云。此乃指其误字改处。非谓当割裂全篇也。且其启学者不敬之心之教。盖已严立堤防。而今乃改易其文字。变换其意趣。自作纷乱之證。驱率圣贤之言。以成己意。亦已甚矣。(不合改其文云云。乃或者说。今作郑氏说亦可怪。)大抵锡鼎前后援引者。或剟取句语之近似。或删其首尾。或添以己言。以自文饰。其意盖以谓吾之说张皇罗络。未
度。而妄自纷乱古经而曰。此朱子平生雅志。则岂非诬朱子之甚者乎。(与叶书是指通解。胡居丧时。尝编次丧礼。自始死以至终丧。各立门目。以呈先生。临归教以云云。此则如今丧礼备要之类。与今类编。天壤不侔。)自言悉遵通解义例。而实则全然相反。今不暇一一辨论。而姑举其大者。天子诸侯之礼。决不可相杂。以乱名分。故通解则王朝礼邦国礼。固自各立门户。而今乃合为一套。以致等威无章之弊。(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今编礼尚不识名分之严。而自谓成朱子之雅志。不亦汰哉。)通解中入于学礼者。类编则入于家礼。通解中属于家礼者。类编则别立嘉礼。如此类不胜其夥。然至于所引朱子语考之。本文或问经文不可轻改曰。改经文。固启学者不敬之心。然旧有一人专攻郑康成解礼记。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时术之亦不改。只作蚕蛾子云。如蚕种之生。循环不息。是何义也。且如大学举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义理云。此乃指其误字改处。非谓当割裂全篇也。且其启学者不敬之心之教。盖已严立堤防。而今乃改易其文字。变换其意趣。自作纷乱之證。驱率圣贤之言。以成己意。亦已甚矣。(不合改其文云云。乃或者说。今作郑氏说亦可怪。)大抵锡鼎前后援引者。或剟取句语之近似。或删其首尾。或添以己言。以自文饰。其意盖以谓吾之说张皇罗络。未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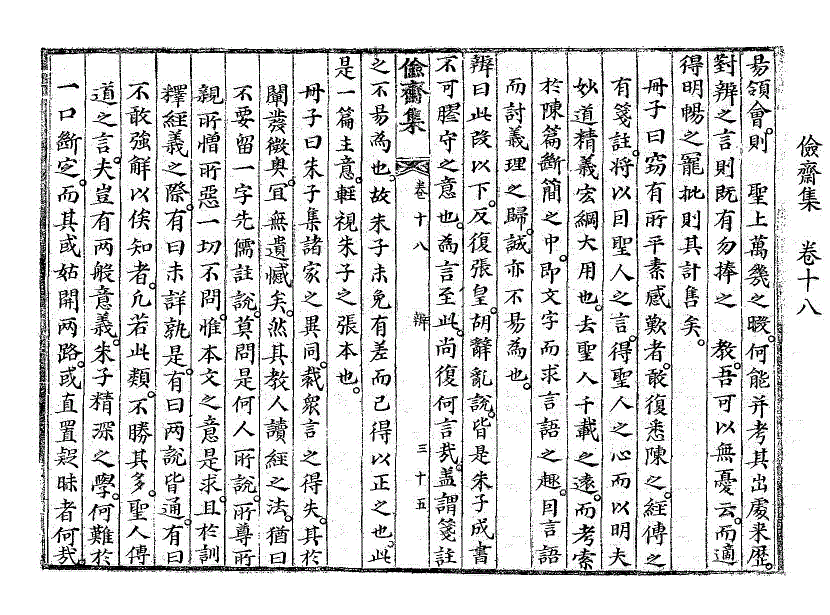 易领会。则 圣上万几之暇。何能并考其出处来历。对辨之言则既有勿捧之 教。吾可以无忧云。而适得明畅之宠批则其计售矣。
易领会。则 圣上万几之暇。何能并考其出处来历。对辨之言则既有勿捧之 教。吾可以无忧云。而适得明畅之宠批则其计售矣。册子曰窃有所平素感叹者。敢复悉陈之。经传之有笺注。将以因圣人之言。得圣人之心而以明夫妙道精义宏纲大用也。去圣人千载之远。而考索于陈篇断简之中。即文字而求言语之趣。因言语而讨义理之归。诚亦不易为也。
辨曰此段以下。反复张皇。胡辞乱说。皆是朱子成书不可胶守之意也。为言至此。尚复何言哉。盖谓笺注之不易为也。故朱子未免有差而已得以正之也。此是一篇主意。轻视朱子之张本也。
册子曰朱子集诸家之异同。裁众言之得失。其于阐发微奥。宜无遗憾矣。然其教人读经之法。犹曰不要留一字先儒注说。莫问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不问。惟本文之意是求。且于训释经义之际。有曰未详孰是。有曰两说皆通。有曰不敢强解以俟知者。凡若此类。不胜其多。圣人传道之言。夫岂有两般意义。朱子精深之学。何难于一口断定。而其或姑开两路。或直置疑昧者何哉。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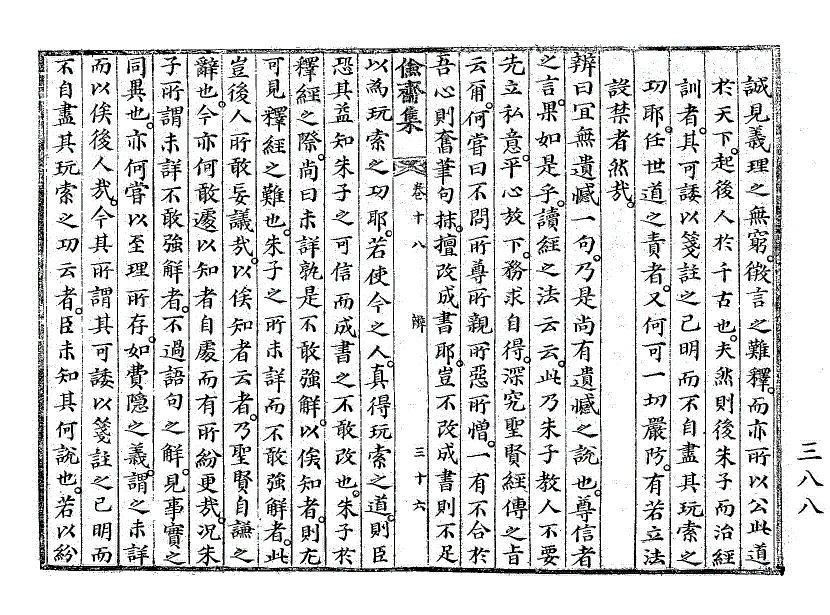 诚见义理之无穷。微言之难释。而亦所以公此道于天下。起后人于千古也。夫然则后朱子而治经训者。其可诿以笺注之已明而不自尽其玩索之功耶。任世道之责者。又何可一切严防。有若立法设禁者然哉。
诚见义理之无穷。微言之难释。而亦所以公此道于天下。起后人于千古也。夫然则后朱子而治经训者。其可诿以笺注之已明而不自尽其玩索之功耶。任世道之责者。又何可一切严防。有若立法设禁者然哉。辨曰宜无遗憾一句。乃是尚有遗憾之说也。尊信者之言。果如是乎。读经之法云云。此乃朱子教人不要先立私意。平心放下。务求自得。深究圣贤经传之旨云尔。何尝曰不问所尊所亲所恶所憎。一有不合于吾心则奋笔句抹。擅改成书耶。岂不改成书则不足以为玩索之功耶。若使今之人。真得玩索之道。则臣恐其益知朱子之可信而成书之不敢改也。朱子于释经之际。尚曰未详孰是不敢强解。以俟知者。则尤可见释经之难也。朱子之所未详而不敢强解者。此岂后人所敢妄议哉。以俟知者云者。乃圣贤自谦之辞也。今亦何敢遽以知者自处而有所纷更哉。况朱子所谓未详不敢强解者。不过语句之解。见事实之同异也。亦何尝以至理所存。如费隐之义。谓之未详而以俟后人哉。今其所谓其可诿以笺注之已明而不自尽其玩索之功云者。臣未知其何说也。若以纷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9H 页
 改背异。谓之玩索则是固不知玩索之为何事。有不足辨矣。若故为此说。以作游辞文饰之计。则其心术之颇僻。不特文义之差而已矣。夫朱子之道。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苟或一有背异于朱子者。固将鸣鼓攻之之不暇矣。董仲舒告于其君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使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又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朱子曰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又曰邪说害正。人人得以攻之。如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以此观之。任世道之责者。其将一任其乱道惑众而莫之严防乎。其将立法设禁而痛绝其萌乎。今日所以导 人主者如此。其祸可胜言哉。朱子曰不讨乱贼而谓人勿讨者。凶逆之党也。不距杨墨而谓人勿距者。禽兽之徒也。呜呼可不惧哉。(孔子曰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改背异。谓之玩索则是固不知玩索之为何事。有不足辨矣。若故为此说。以作游辞文饰之计。则其心术之颇僻。不特文义之差而已矣。夫朱子之道。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苟或一有背异于朱子者。固将鸣鼓攻之之不暇矣。董仲舒告于其君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使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又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朱子曰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又曰邪说害正。人人得以攻之。如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以此观之。任世道之责者。其将一任其乱道惑众而莫之严防乎。其将立法设禁而痛绝其萌乎。今日所以导 人主者如此。其祸可胜言哉。朱子曰不讨乱贼而谓人勿讨者。凶逆之党也。不距杨墨而谓人勿距者。禽兽之徒也。呜呼可不惧哉。(孔子曰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册子曰先贤之言明备。而后学未能透悟而起疑者有之。或先贤之言有未尽释。而有待于后人之阐明者有之。故程子曰解经不同无害。又曰学者先要会疑。其次渐有疑。其次节节有疑。张子曰其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89L 页
 解经而未尽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以此论之则后学之于经传训义。录其疑而求正可也。发其未尽处而阐明亦可也。
解经而未尽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以此论之则后学之于经传训义。录其疑而求正可也。发其未尽处而阐明亦可也。辨曰学问之道。小疑则小益。大疑则大益。故程子之训。欲令学者会疑而深思耳。何尝令不信圣贤而妄改成书乎。(按其次渐有疑以下。乃朱子之言。而此并以为程子说。亦可怪。此等误引。亦可见其粗率之一端。何足以论经传之奥义乎。)解经不同无害者。亦谓训诂名目之间也。如皇极之解作大中。复辟之解作复君。如今从周寡过之说。岂不大害于义乎。张子之言。亦谓不善者共改之。何尝谓不问善不善。妄立己见。纷纷不已乎。且改不善二字。作解经未尽。以文己说。不亦异乎。若使学者不肯低头下心。深究圣贤之旨。而惟以涂改成书为务曰解经不同无害也。不善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云尔。则其流之弊。何可胜言。正长其浮薄不逊之心耳。此岂程张教人之本意哉。
册子曰朱子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闻道之方。固有二端。而穷理之术。盖亦相符。徒能笃信注说而不知反求。则无以深造自得而终为殆罔之归矣。由是论之。传注文字虽无一字之可疑。犹未害于设为疑难。自致反求之功。况先贤所自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0H 页
 为说。深有望于后学者耶。今以一二辨论。谓之僭逼先贤。稍有差殊于传注则张目呵禁。惟恐触犯。是则以反求不如笃信。而曾子不及子夏也。
为说。深有望于后学者耶。今以一二辨论。谓之僭逼先贤。稍有差殊于传注则张目呵禁。惟恐触犯。是则以反求不如笃信。而曾子不及子夏也。辨曰曾子子夏之事。有何毫发干涉于毁经乱道而有此引援耶。(闻道以下。锡鼎自下之说也。亦可见妆撰之迹矣。)曾子亦尝有不信孔子而追改孔子之成书者耶。此等说有若梦中呓言。全不着题矣。先贤深有望于后学者。岂以倒戈相攻坏乱经旨相望耶。差殊于传注则是邪说也。不为张目呵禁而何哉。纷改成书。果为一二辨论耶。(每以纷改归之于反求设疑此等处。不可胜辨。)
册子曰先儒陈栎之言曰宁为朱子之忠臣。不为朱子之佞臣。古之有志于经训者。其意盖如此。故王柏,饶鲁,金履祥诸儒皆朱门淑艾之人。而其于篇章之合分。学问之规范。不遵闽中之绪言者多矣。是岂务立新奇。甘心违异而然哉。诚以学术者天下之公物。经传者天下之公案。务自尽乎反复深造之功。而亦深体乎先贤开导后学之意也。然而后之笃论者。或称以朱门之嫡传。或许以宋季之名儒。乌有所谓毁经侮贤之名也哉。
辨曰定宇之说。乃自明其言之有功朱子。而非出阿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0L 页
 好苟合之意也。何可引而班之于饶王诸人乎。若使定宇背异纷改如今日则是乃反贼也。岂曰忠臣。按其本传曰栎尝谓朱先生没未久而诸家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礼记集义等书。凡有畔于朱子者。刊而去之。于是朱子之说大行于世。吴草庐亦称栎有功于朱子为大。其为朱子之忠臣。盖如是而已。此果可为今日之證乎。若曰涂改成书而后可为忠臣。则张汤之纷更高皇帝约束。乃为汉世之忠臣。而周公之无作聪明乱旧章。未免为周室之佞臣耶。(以一遵朱子为佞臣。尤极痛心。)至于饶王诸人则当时已议其非。后世亦诛其僭。盖饶书牴牾于朱子。而胡云峰著书以正之。李滉尝论王氏曰此老本有好奇立异之病。又曰王鲁斋学术多病。又曰适得破经之罪。先贤所以明辨峻斥如此。而今以为乌有毁经侮贤之名何也。鲁斋人心道心说。亦见于心经附注。而语多未莹。有不足与论于精微之蕴。则其学可知也。其不识朱子。甘心违异也宜矣。今之所慕者饶王。故每每称引。不欲指斥其失而乃以此援朋挈党。共议朱子。其向背如此则亦可谓下乔木而入幽谷也。(称以嫡传许以名儒。是谁之笃论。未之前闻也。)若以为学术公物。经传公案。而人人得以议之。
好苟合之意也。何可引而班之于饶王诸人乎。若使定宇背异纷改如今日则是乃反贼也。岂曰忠臣。按其本传曰栎尝谓朱先生没未久而诸家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礼记集义等书。凡有畔于朱子者。刊而去之。于是朱子之说大行于世。吴草庐亦称栎有功于朱子为大。其为朱子之忠臣。盖如是而已。此果可为今日之證乎。若曰涂改成书而后可为忠臣。则张汤之纷更高皇帝约束。乃为汉世之忠臣。而周公之无作聪明乱旧章。未免为周室之佞臣耶。(以一遵朱子为佞臣。尤极痛心。)至于饶王诸人则当时已议其非。后世亦诛其僭。盖饶书牴牾于朱子。而胡云峰著书以正之。李滉尝论王氏曰此老本有好奇立异之病。又曰王鲁斋学术多病。又曰适得破经之罪。先贤所以明辨峻斥如此。而今以为乌有毁经侮贤之名何也。鲁斋人心道心说。亦见于心经附注。而语多未莹。有不足与论于精微之蕴。则其学可知也。其不识朱子。甘心违异也宜矣。今之所慕者饶王。故每每称引。不欲指斥其失而乃以此援朋挈党。共议朱子。其向背如此则亦可谓下乔木而入幽谷也。(称以嫡传许以名儒。是谁之笃论。未之前闻也。)若以为学术公物。经传公案。而人人得以议之。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1H 页
 人人得以改之。则群圣贤之书。宁有不被其害者乎。即此一心。已足以祸天下国家矣。且方称扬饶王。以为无背朱子。而乃反谓学问规范。不遵闽中。则是不觉失笑处也。圣贤之为学。犹大匠之治木。自有不易之规矩。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也。臣未闻学问规范异于圣贤而能为学问者也。规范既异则是异端也。此岂篇章合分。互相异同之伦。而今乃对举而比论之。其初不识学问规范之实。据此可知矣。以如此之见识。妄论朱子之得失。其亦可哀也已。
人人得以改之。则群圣贤之书。宁有不被其害者乎。即此一心。已足以祸天下国家矣。且方称扬饶王。以为无背朱子。而乃反谓学问规范。不遵闽中。则是不觉失笑处也。圣贤之为学。犹大匠之治木。自有不易之规矩。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也。臣未闻学问规范异于圣贤而能为学问者也。规范既异则是异端也。此岂篇章合分。互相异同之伦。而今乃对举而比论之。其初不识学问规范之实。据此可知矣。以如此之见识。妄论朱子之得失。其亦可哀也已。册子曰朱子之为传注也。广采诸家。不没片善。不问其人之善否。处地之轻重。惟其言之允当是取。虽素尝攻贬如王安石,苏轼。名称轻微如洪兴租,吴棫。苟其言之有中则不厌论载。其在门人晚进之质难。知旧凡材之往复。亦莫不虚心采纳。尽乎人言。其规模之宽大。胸次之公平。有如是者。推此志也。藉令王金之说。质问于朱子之平生。则其必有一二印可而不至于麾呵斥绝矣。论者未睹大体。不究经传之本末。不察先贤之心迹。惟是一言半辞违覆于朱门。则大忧以惧。若犯大讳。此虽心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1L 页
 无挟杂。恐未免为太伤于拘滞也。
无挟杂。恐未免为太伤于拘滞也。辨曰朱子尝曰君子不以人废言。言有可取。安得不取。故其为传注也。不问其人之贤否。惟其言之是取。盖以其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知之真而择之明故耳。今乃以不逮之见。追论于千载之下曰。藉令质问于平日则必有印可。又从而涂改成书而不少疑难。不几于纵恣无忌惮耶。朱子尝与南轩论程子文集改字曰。圣贤成书。稍有不惬己意处。便率情奋笔。恣行涂改。恐此气像亦自不佳。所改虽善。犹启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又曰汉儒释经。有欲改易处。但云某当作某。后世犹或非之。况遽改乎。非特汉儒而已。孔子删书。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继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终不刊去此文。以从己意之便也。又曰前圣入太庙。每事问。存饩羊谨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闻阙疑之心为如何。今日纷更专辄之意象。又为如何云云。其谨守成书。不欲纷更之意。至于如此。此岂由于规模不宽大。胸次不公平而然哉。惜乎锡鼎之不闻此义也。稍有志于尊贤卫道者。见此斯文之变怪而不知惊惧。非人情也。此岂可以拘滞斥之哉。且其若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2H 页
 犯大讳。惟恐触犯等说。有若朱子真有可讳之过。而为其所攻发。故今之言者。皆阿好掩讳。惟恐其或彰者然。吁亦痛矣。
犯大讳。惟恐触犯等说。有若朱子真有可讳之过。而为其所攻发。故今之言者。皆阿好掩讳。惟恐其或彰者然。吁亦痛矣。册子曰虽以我东褊隘之俗。如李彦迪,赵翼亦尊信朱子之人。而大学补遗诸经浅说。未免有差殊于注说。亦岂欲甘心违异而起疑求质。不害于尊信其道耳。然不闻有深攻力诋如今日之为。
辨曰二臣之书。李滉,朴世采之论详矣。然彦迪之书出于身后。赵翼之书乃是劄录。自成私书者。与擅改先贤成书者有异。然犹且见斥于当时。见非于后贤则何可谓之无攻诋者乎。况今日之事。万万非李赵二臣之比耶。(李滉答李湛书。略曰今献汇言以大学知止等数节。为格物致知章之错简。欲掇此而补彼。所引先儒诸说备矣。滉曩见权阳村入学图说有此说。续见宋史王鲁斋本传。亦云曾有此说。近又见李玉山先生论此甚力。心每疑之。若不明言则犹恐其说之能惑人。故略言之。纲领条目之中。虽无二字。一见于纲领之结。犹未足。再见于条目之结者。诚以学者于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则其于修己治人之道。皆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倒行而逆施之。故丁宁致意如此。传者至此。亦特举二字而释之。则所谓先后终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纲目中无二字。而谓不当传而释之。可谓不思之甚也。适有徒见此数节中有知止知先后知本等语。意谓可移之为格物之传。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云云。阳村权近号。玉山李彦迪号。○朴世采答翼孙持恒书。略曰行状文字。谨因所签改呈。其间亦有新加添删者。幸乞垂察。惟其论著一款。观诸公意思。或初不详考。或已颇知其重大。皆不说肯綮。盖由未见遗书本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2L 页
 文也。惟鄙作行状时。未及勘阅。姑依议论异同一边而考正之而已。今见本书体模。宛一文公四书集注章句。此则恐其弊不止于所谓议论异同也。尝谓朱子既定著集注章句。以为万世道学规模。精深简奥。攧扑不破。其在后学。惟当深味而谨守之耳。或有意见稍别者。亦当各就所知处。略加劄录。以俟后来之君子。则此王金饶胡之说。虽甚未安。犹不至圣门之大罪者也。今遗书则不然。其部伍论解。自成一家。殆与文公旧注势抗力敌。莫分主客。无论义理得失之辨。即其事体之臲
文也。惟鄙作行状时。未及勘阅。姑依议论异同一边而考正之而已。今见本书体模。宛一文公四书集注章句。此则恐其弊不止于所谓议论异同也。尝谓朱子既定著集注章句。以为万世道学规模。精深简奥。攧扑不破。其在后学。惟当深味而谨守之耳。或有意见稍别者。亦当各就所知处。略加劄录。以俟后来之君子。则此王金饶胡之说。虽甚未安。犹不至圣门之大罪者也。今遗书则不然。其部伍论解。自成一家。殆与文公旧注势抗力敌。莫分主客。无论义理得失之辨。即其事体之臲册子曰臣所编述者。固皆取裁于朱子义例。折衷于先正绪言。而其他一二处。不过章段之浅近。字句之纤琐。
辨曰删抹篇题。添以他说。本末章之合并。费隐章之附录。孝经之扫去刊误。岂浅近纤琐者耶。且上文则缕缕为说。有若微辞奥义不可不明。故不得不改。而至此则乃以为浅近纤琐。又何其言之衡决耶。
册子曰程子撰易传之后。举世无一人议其文义。而朱子本义多有牴牾。是举世皆尊信程子。而独朱子不尊信乎哉。朱子诗书传及论孟集注庸学章句。举世无一人论其文义。而饶王诸人及李赵两臣。有所论及。是举世皆尊信朱子。而独饶王李赵为不尊信乎哉。惟其笃信积功。故反求而质其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3H 页
 所疑焉耳。由是言之。尊信朱子而师其道。不规规于文义异同之粗迹而深得先贤之意。务求古经之旨。乃为真尊信也。
所疑焉耳。由是言之。尊信朱子而师其道。不规规于文义异同之粗迹而深得先贤之意。务求古经之旨。乃为真尊信也。辨曰周易自是卜筮之书。而孔子始取而敷绎说出道理。故程子之传从义理。朱子本义从卜筮。初非牴牾而然也。岂若饶王诸公之好新立异者哉。今乃援朱子而等夷之。则不知朱子甚矣。朱子曰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程传本义之不同。亦犹是也。且饶王诸公虽曰好新立异。何曾以己意直改成书。如今日之为耶。然则饶王亦非今日之伦比也。抑朱子之于群贤。所谓集大成者也。设有点改易传之事。决非后人所敢效拟。未知今之人。其于朱子。亦以朱子之于程子自处耶。立心如此则将何所不至哉。朱子之道。于今可见者。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今乃视成书为粗迹。不欲规规尊信。而妄以私意擅行窜易。自谓深得先贤之意。肆然笔之于告君之辞。独不畏百世之公议乎。
册子曰金载白疏有曰补亡章。朱子之苦心极力。惟在于此。乃敢段段分割。妄附新注云云。夫朱子之苦心专在补亡章云此固然矣。第章句刊行。本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3L 页
 不入于分章之内而附列于传释之左方。不分各段。合为一通文字。此固出于朱夫子自谦之意。而后学之尊敬表章。其体自别。故谨就补亡本文。分为五段。推演章句之意。附注于诸段之下。以备传注之体。臣之积年苦心。亦专在于此。今以僭妄无严斥之何也。又曰大学格致传。独为阙脱。故朱子作为文字。以补其缺。后儒论说多端。疑难不一。如王守仁别生新义。角立于考亭者。固无论已。如董槐,叶梦鼎,蔡清,宋濂,方孝孺诸人。皆尊崇朱子之人。而亦不能恪遵而深信。虽以李彦迪之尊信朱子。亦取经文二章。以补阙脱。而朱子一生苦心用力之文字。自归删没。
不入于分章之内而附列于传释之左方。不分各段。合为一通文字。此固出于朱夫子自谦之意。而后学之尊敬表章。其体自别。故谨就补亡本文。分为五段。推演章句之意。附注于诸段之下。以备传注之体。臣之积年苦心。亦专在于此。今以僭妄无严斥之何也。又曰大学格致传。独为阙脱。故朱子作为文字。以补其缺。后儒论说多端。疑难不一。如王守仁别生新义。角立于考亭者。固无论已。如董槐,叶梦鼎,蔡清,宋濂,方孝孺诸人。皆尊崇朱子之人。而亦不能恪遵而深信。虽以李彦迪之尊信朱子。亦取经文二章。以补阙脱。而朱子一生苦心用力之文字。自归删没。辨曰今以自己注说。偃然参错于大贤成书之中。实为僭妄。而儒疏所斥。乃指其欲以附注视同章句。为经筵进讲科试帖括之用耳。今不答此而广引董文靖诸人。以为致疑于章句之證。游辞漫说以乱真伪。诚可痛也。至若儒疏谓朱子苦心极力惟在于此。则今亦自谓积年苦心。亦专在此。欲与朱子并峙而相抗。呜呼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册子曰前后诸疏中。每以非如箧笥私藏为言。又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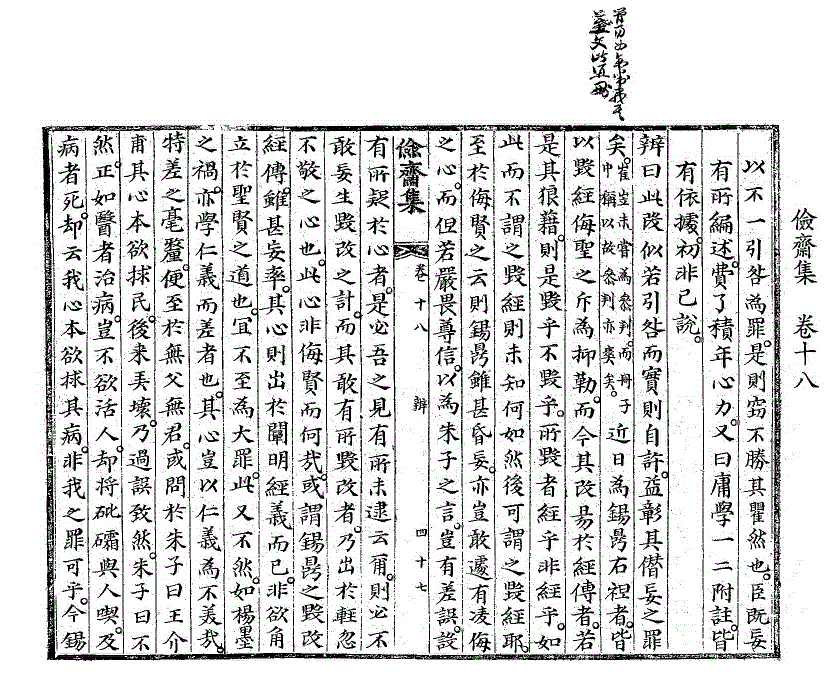 以不一引咎为罪。是则窃不胜其瞿然也。臣既妄有所编述。费了积年心力。又曰庸学一二附注。皆有依据。初非己说。
以不一引咎为罪。是则窃不胜其瞿然也。臣既妄有所编述。费了积年心力。又曰庸学一二附注。皆有依据。初非己说。辨曰此段似若引咎而实则自许。益彰其僭妄之罪矣。(崔岦未尝为参判。而册子中称以故参判亦爽矣。)近日为锡鼎右袒者。皆以毁经侮圣之斥为抑勒。而今其改易于经传者。若是其狼藉。则是毁乎不毁乎。所毁者经乎非经乎。如此而不谓之毁经则未知何如然后可谓之毁经耶。至于侮贤之云则锡鼎虽甚昏妄。亦岂敢遽有凌侮之心。而但若严畏尊信。以为朱子之言。岂有差误。设有所疑于心者。是必吾之见有所未逮云尔。则必不敢妄生毁改之计。而其敢有所毁改者。乃出于轻忽不敬之心也。此心非侮贤而何哉。或谓锡鼎之毁改经传。虽甚妄率。其心则出于阐明经义而已。非欲角立于圣贤之道也。宜不至为大罪。此又不然。如杨墨之祸。亦学仁义而差者也。其心岂以仁义为不美哉。特差之毫釐。便至于无父无君。或问于朱子曰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后来弄坏。乃过误致然。朱子曰不然。正如医者治病。岂不欲活人。却将砒礵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非我之罪可乎。今锡
俭斋集卷之十八 第 394L 页
 鼎之心。纵使出于阐明经义。其不知而妄作。已难免僭踰乱道之诛。(王安石新经。亦自欲阐明经义也。)况其心初出于好新求异。誇多斗靡。而非有意于经义者乎。(此非臣抑勒之说也。观其辄以王柏饶鲁自比而不欲尊信朱子。则其好新求异可知也。观其所引诸说。全不着题。而旁揽广援。以为眩乱之计。则其誇多斗靡可知也。其心如此则非有意于经义可知也。)今又广引圣贤之言。任意删节。掠取片辞单言。互换文饰。以为口给御人之资。则其心术之所由起。公乎私乎。邪乎正乎。或谓此寔出于见识之不明耳。若以为毁经侮贤之罪则不亦过乎。臣又应之曰从古异端邪说。亦由于见识之差者。而朱子尝谓安石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也。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也。(差与不差而舜蹠分矣。此锡鼎所以必欲删差字于篇题者也。)夫见道理透彻与否。固不足拟论于今日。而今以粗浅之见。不肯谨守成训。而辄乃毁改经传。以犯春秋大一统之义。真所谓不知春秋之义则为善为之必陷于首恶之诛者也。是乌得为无罪乎。(自有此事。上以成君父之过举。下以溺一世之人心。目前之祸。亦不可谓不深矣。)
鼎之心。纵使出于阐明经义。其不知而妄作。已难免僭踰乱道之诛。(王安石新经。亦自欲阐明经义也。)况其心初出于好新求异。誇多斗靡。而非有意于经义者乎。(此非臣抑勒之说也。观其辄以王柏饶鲁自比而不欲尊信朱子。则其好新求异可知也。观其所引诸说。全不着题。而旁揽广援。以为眩乱之计。则其誇多斗靡可知也。其心如此则非有意于经义可知也。)今又广引圣贤之言。任意删节。掠取片辞单言。互换文饰。以为口给御人之资。则其心术之所由起。公乎私乎。邪乎正乎。或谓此寔出于见识之不明耳。若以为毁经侮贤之罪则不亦过乎。臣又应之曰从古异端邪说。亦由于见识之差者。而朱子尝谓安石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也。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也。(差与不差而舜蹠分矣。此锡鼎所以必欲删差字于篇题者也。)夫见道理透彻与否。固不足拟论于今日。而今以粗浅之见。不肯谨守成训。而辄乃毁改经传。以犯春秋大一统之义。真所谓不知春秋之义则为善为之必陷于首恶之诛者也。是乌得为无罪乎。(自有此事。上以成君父之过举。下以溺一世之人心。目前之祸。亦不可谓不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