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x 页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序
序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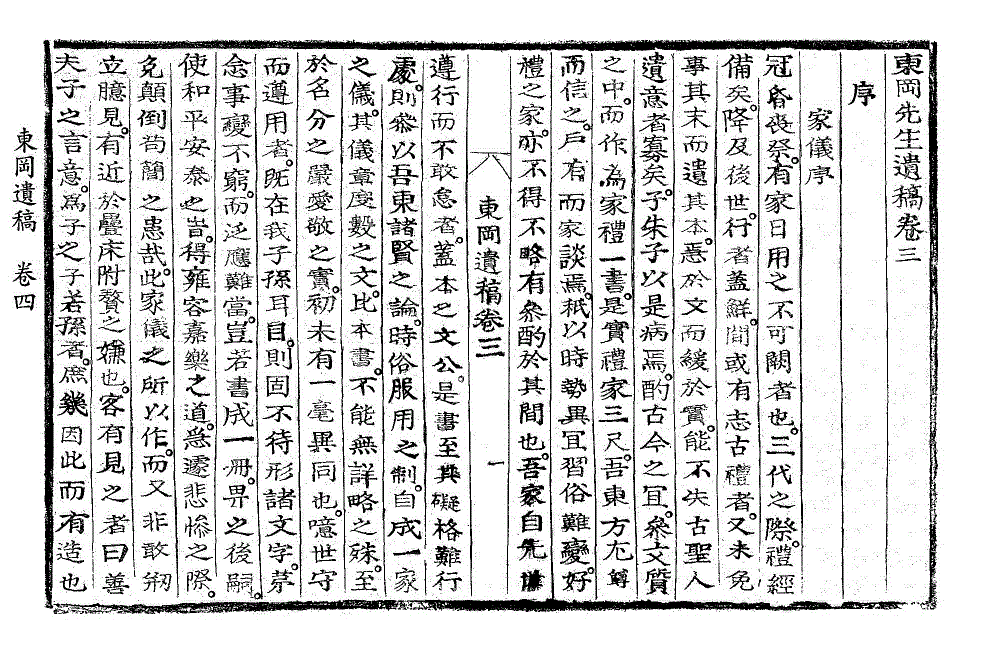 家仪序
家仪序冠昏丧祭。有家日用之不可阙者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降及后世。行者盖鲜。间或有志古礼者。又未免事其末而遗其本。急于文而缓于实。能不失古圣人遗意者寡矣。子朱子以是病焉。酌古今之宜。参文质之中。而作为家礼一书。是实礼家三尺。吾东方尤尊而信之。户有而家谈焉。秖以时势异宜习俗难变。好礼之家。亦不得不略有参酌于其间也。吾家自先世遵行而不敢怠者。盖本之文公。是书至其碍格难行处。则参以吾东诸贤之论。时俗服用之制。自成一家之仪。其仪章度数之文。比本书。不能无详略之殊。至于名分之严爱敬之实。初未有一毫异同也。噫世守而遵用者。既在我子孙耳目。则固不待形诸文字。第念事变不穷。而泛应难当。岂若书成一册。畀之后嗣。使和平安泰之时。得雍容嘉乐之道。急遽悲惨之际。免颠倒苟简之患哉。此家仪之所以作。而又非敢刱立臆见。有近于叠床附赘之嫌也。客有见之者曰善夫子之言意。为子之子若孙者。庶几因此而有造也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3L 页
 哉。余曰未也。古人所以贻厥后者。非不多且大也。能守而不失者鲜矣。况此一片文字。宁有关于子孙贤不肖乎。又安知夫不惟不遵而已。乃有裂而涂诸壁者乎。客曰子之虑后也过矣。安知夫有贤子孙。以子之所今草刱者。能成修饰润色之美。永有辞于来许乎。余乃哂而书之卷首。使后之为子孙者。视以为劝戒焉。(乙丑六月)
哉。余曰未也。古人所以贻厥后者。非不多且大也。能守而不失者鲜矣。况此一片文字。宁有关于子孙贤不肖乎。又安知夫不惟不遵而已。乃有裂而涂诸壁者乎。客曰子之虑后也过矣。安知夫有贤子孙。以子之所今草刱者。能成修饰润色之美。永有辞于来许乎。余乃哂而书之卷首。使后之为子孙者。视以为劝戒焉。(乙丑六月)龙城志序
地之有志。盖古也。一邑则有一邑之志。一国则有一国之志。天下则有天下之志。地而无志。山川之形势。人物之盛衰。古今之事迹。无以知其实矣。视邑而知国。视国而知天下。邑志之有关于天下国家亦大矣。粤自轩辕昼野。夏禹敷土。地道经纬始矣。降及秦汉。迄于唐宋。则既有图籍。且有志记。天文之分野。自各有所属矣。逮夫大明一统。宇内同轨。偏方小邑。莫不有图志。人事之制度。至是而又该尽矣。地志一书。而三才之理具焉。古人立言诏后之意。夫岂偶然哉。惟我青丘。僻在海隅。檀君以前。文献无徵。箕子东临。始兴文教。而至于志籍。犹未也。历三国至高丽。则地志名目。或见于传记。而全书不存。故虽以权阳村之博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4H 页
 洽。其论三韩疆界。与崔文昌所言。大相径庭。使后人莫可适从。是岂非东方一欠事耶。暨我 成庙之十年。始命卢思慎等。因梁诚之,徐居正所进地志及东文选。辑成舆地胜览。至 中庙朝。又令李荇等。续编而增修之。今我 圣上。乃更监先王之成宪。念后代之无稽。申 命廷臣。颁教中外。取近世事以新增之。于是四方八道。前后实迹。一开卷而森罗。尽在目中。 列圣之羽翼治道者。吁其至矣。第以其书编帙浩多。于列邑事。有难纤悉。只各举其梗槩。此又邑志之所以作也。念玆龙城。本百济旧场也。而带方古国也。处湖岭之要冲。作邦家之保障。东北而控智异八公之崧高。西南而带鹑津鸭江之泓澄。幅员之大数百馀里。部坊之多四十有五。其关防之壮。形胜之饶。物产之富。甲于湖中。真所谓维南右臂。天府之地也。地灵人杰。奎文钟英之称。又是实录也。噫江山自在而人事易改。不知中间阅几番沿革。更几度世变哉。今以书中所载者言之。忠臣贤士。有殂豆之祠院。孝子烈女。有门闾之绰楔。城池府库。所以待㬥客而备上供也。寺馆楼亭。所以接行旅而资游观也。以至田结户口之多少。山川道路之远近。姓氏之所自。丘墓之
洽。其论三韩疆界。与崔文昌所言。大相径庭。使后人莫可适从。是岂非东方一欠事耶。暨我 成庙之十年。始命卢思慎等。因梁诚之,徐居正所进地志及东文选。辑成舆地胜览。至 中庙朝。又令李荇等。续编而增修之。今我 圣上。乃更监先王之成宪。念后代之无稽。申 命廷臣。颁教中外。取近世事以新增之。于是四方八道。前后实迹。一开卷而森罗。尽在目中。 列圣之羽翼治道者。吁其至矣。第以其书编帙浩多。于列邑事。有难纤悉。只各举其梗槩。此又邑志之所以作也。念玆龙城。本百济旧场也。而带方古国也。处湖岭之要冲。作邦家之保障。东北而控智异八公之崧高。西南而带鹑津鸭江之泓澄。幅员之大数百馀里。部坊之多四十有五。其关防之壮。形胜之饶。物产之富。甲于湖中。真所谓维南右臂。天府之地也。地灵人杰。奎文钟英之称。又是实录也。噫江山自在而人事易改。不知中间阅几番沿革。更几度世变哉。今以书中所载者言之。忠臣贤士。有殂豆之祠院。孝子烈女。有门闾之绰楔。城池府库。所以待㬥客而备上供也。寺馆楼亭。所以接行旅而资游观也。以至田结户口之多少。山川道路之远近。姓氏之所自。丘墓之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4L 页
 所在。土产之有无。风俗之污隆。无不具录。且其志士高人之懿行异迹。诗流词客之丽语佳韵。旁搜曲采。靡有疏漏。凡诸境内自古至今。巨细事实。昭然若烛照数计。无所疑晦。非如胜览全书之举大而遗小。记略而欠详也。呜呼观此志者。孝悌忠信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见祠院则思忠贤而授命践形之是期。见绰楔则思孝烈而竭力尽节之是效。见城池府库。则思先王之所经理。而遵守之道。不宜忽也。见寺观楼亭。则思前辈之尝去来。而感慕之情。自不已也。田结以之应贡赋。则先私后公之心。不敢萌也。户口以之籍民数。则哀穷恤贫之义。不可忘也。至于见山川之流峙。则思仁智之有𧗱。见道路之纵横。则思趋向之必正。见姓氏所自。则尊祖睦宗之谊。罔或缺矣。见丘墓所在。则报本追远之诚。莫或怠矣。土产之有无不齐。则可验物理之难全也。风俗之污隆不同。则可戒人心之易陷也。况复前人懿行异迹。丽语佳韵。莫不有以启发其良心而兴起其善端。则邑志之有补于世道者。岂特口耳文字间而已哉。呜呼。天高地下。人处乎其间。天地无穷。而人生也有涯。百年光阴。无异草头之朝露矣。虽然天地无为而吾人有为。立德乎
所在。土产之有无。风俗之污隆。无不具录。且其志士高人之懿行异迹。诗流词客之丽语佳韵。旁搜曲采。靡有疏漏。凡诸境内自古至今。巨细事实。昭然若烛照数计。无所疑晦。非如胜览全书之举大而遗小。记略而欠详也。呜呼观此志者。孝悌忠信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见祠院则思忠贤而授命践形之是期。见绰楔则思孝烈而竭力尽节之是效。见城池府库。则思先王之所经理。而遵守之道。不宜忽也。见寺观楼亭。则思前辈之尝去来。而感慕之情。自不已也。田结以之应贡赋。则先私后公之心。不敢萌也。户口以之籍民数。则哀穷恤贫之义。不可忘也。至于见山川之流峙。则思仁智之有𧗱。见道路之纵横。则思趋向之必正。见姓氏所自。则尊祖睦宗之谊。罔或缺矣。见丘墓所在。则报本追远之诚。莫或怠矣。土产之有无不齐。则可验物理之难全也。风俗之污隆不同。则可戒人心之易陷也。况复前人懿行异迹。丽语佳韵。莫不有以启发其良心而兴起其善端。则邑志之有补于世道者。岂特口耳文字间而已哉。呜呼。天高地下。人处乎其间。天地无穷。而人生也有涯。百年光阴。无异草头之朝露矣。虽然天地无为而吾人有为。立德乎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5H 页
 身。参天地而赞化育者人也。立功立言。与天地相终始者亦人也。自龙城有邑以来。生且死于其间者。不知几千万。而同一归于澌尽泯灭。其能卓然有立。流名不朽者。有几人耶。然则后此而生者。岂不别有感于斯文乎。近观名州大镇。或多有志。而独此府无存。壬丁兵燹。盖有以致之也。邑人之茹叹久矣。乃者地主李公耇徵因 朝命。议于众曰此事必得人乃可。谁可任者。佥曰李君焘,崔君与天其人。于是两君实主张而始终之。祗慎无怠。贤劳累月。既修进胜览新增之文。仍又推演。别成邑志。其凡例格式。则博考诸州所作。折衷而取其长。方谋锓梓。以寿其传。而属余作文以弁之。余辞以袜绵。其请益苛。谨受而阅之。不但其所辑录。尽可考徵。先生长老之言行篇什。咸萃于此。而我先代遗迹。亦在其中。不佞之于是书。所感深矣。既不敢当。又不敢辞。抚卷踌躇。遂染翰而为之书。(己卯)
身。参天地而赞化育者人也。立功立言。与天地相终始者亦人也。自龙城有邑以来。生且死于其间者。不知几千万。而同一归于澌尽泯灭。其能卓然有立。流名不朽者。有几人耶。然则后此而生者。岂不别有感于斯文乎。近观名州大镇。或多有志。而独此府无存。壬丁兵燹。盖有以致之也。邑人之茹叹久矣。乃者地主李公耇徵因 朝命。议于众曰此事必得人乃可。谁可任者。佥曰李君焘,崔君与天其人。于是两君实主张而始终之。祗慎无怠。贤劳累月。既修进胜览新增之文。仍又推演。别成邑志。其凡例格式。则博考诸州所作。折衷而取其长。方谋锓梓。以寿其传。而属余作文以弁之。余辞以袜绵。其请益苛。谨受而阅之。不但其所辑录。尽可考徵。先生长老之言行篇什。咸萃于此。而我先代遗迹。亦在其中。不佞之于是书。所感深矣。既不敢当。又不敢辞。抚卷踌躇。遂染翰而为之书。(己卯)朔宁崔氏宗会序
上之三十有三年冬十月丁酉。㠉梁崔氏。会于广州南汉之天柱寺。为叙族也。念我崔氏。即平章先祖之后裔也。溯而论之。邃古生人之初。我始祖想应降于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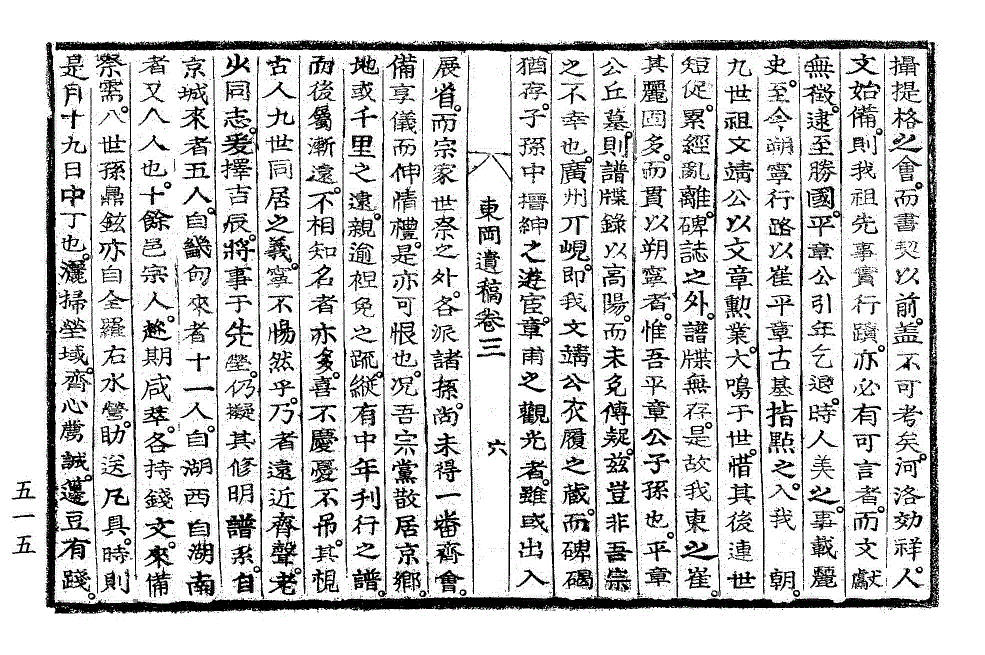 摄提格之会。而书契以前。盖不可考矣。河洛效祥。人文始备。则我祖先事实行迹。亦必有可言者。而文献无徵。逮至胜国。平章公引年乞退。时人美之。事载丽史。至今朔宁行路以崔平章古基指点之。入我 朝。九世祖文靖公以文章勋业。大鸣于世。惜其后连世短促。累经乱离。碑志之外。谱牒无存。是故我东之崔。其丽固多。而贯以朔宁者。惟吾平章公子孙也。平章公丘墓。则谱牒录以高阳。而未免传疑。玆岂非吾宗之不幸也。广州丌岘。即我文靖公衣履之藏。而碑碣犹存。子孙中搢绅之游宦。章甫之观光者。虽或出入展省。而宗家世祭之外。各派诸孙。尚未得一番齐会。备享仪而伸情礼。是亦可恨也。况吾宗党散居京乡。地或千里之逮。亲逾袒免之疏。纵有中年刊行之谱。而后属渐远。不相知名者亦多。喜不庆忧不吊。其视古人九世同居之义。宁不惕然乎。乃者远近齐声。老少同志。爰择吉辰。将事于先茔。仍拟其修明谱系。自京城来者五人。自畿甸来者十一人。自湖西自湖南者又八人也。十馀邑宗人。趁期咸萃。各持钱文。来备祭需。八世孙鼎铉亦自全罗右水营。助送凡具。时则是月十九日中丁也。洒扫茔域。齐心荐诚。笾豆有践。
摄提格之会。而书契以前。盖不可考矣。河洛效祥。人文始备。则我祖先事实行迹。亦必有可言者。而文献无徵。逮至胜国。平章公引年乞退。时人美之。事载丽史。至今朔宁行路以崔平章古基指点之。入我 朝。九世祖文靖公以文章勋业。大鸣于世。惜其后连世短促。累经乱离。碑志之外。谱牒无存。是故我东之崔。其丽固多。而贯以朔宁者。惟吾平章公子孙也。平章公丘墓。则谱牒录以高阳。而未免传疑。玆岂非吾宗之不幸也。广州丌岘。即我文靖公衣履之藏。而碑碣犹存。子孙中搢绅之游宦。章甫之观光者。虽或出入展省。而宗家世祭之外。各派诸孙。尚未得一番齐会。备享仪而伸情礼。是亦可恨也。况吾宗党散居京乡。地或千里之逮。亲逾袒免之疏。纵有中年刊行之谱。而后属渐远。不相知名者亦多。喜不庆忧不吊。其视古人九世同居之义。宁不惕然乎。乃者远近齐声。老少同志。爰择吉辰。将事于先茔。仍拟其修明谱系。自京城来者五人。自畿甸来者十一人。自湖西自湖南者又八人也。十馀邑宗人。趁期咸萃。各持钱文。来备祭需。八世孙鼎铉亦自全罗右水营。助送凡具。时则是月十九日中丁也。洒扫茔域。齐心荐诚。笾豆有践。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6H 页
 昭穆有序。祭毕将修谱。以村舍狭隘。并辔向寺门西行十馀里。由东城而入。达于所谓天柱寺者。寺藏城西最高峰下。城中凡有九寺。而坐地眼界此为最云。团圆一堂。接膝连袂。乃取前印之谱本。更记后孙之名字。以为增刊广传之地。而沽取松醪。各倾数杯。舒古情之绸缪。吐新语之阑珊。于时积雨初收。霁景方明。相与联翩步陟寺后峰。登所谓上将台。四面轩豁。无所障碍。远近江山。总入眼底。前临粉堞。尚记古国之城郭。(此地即百济始祖温祚古城。)俯瞰沙场。缅忆忠魂之愤郁。遂皆徘徊散步。慷慨悲吟。龙城崔是翁。乃抚釰雪涕。中坐而言曰行宫枕戈。呜呼前王不忘。含香执靮。忍想先子遗踪。(我祖考丙子。以左承旨扈 驾。故 赐祭文。有执靮捍王等语。)山川不改。人事易变。当时事迹。恍如昨日。而屈指于今。奄成七十二年矣。嗟夫士生天地间。忠与孝而已。非忠无君。非孝无亲。今吾侪得保旧业之青毡。能守世传之素节者。莫非吾祖先之德荫也。优游以乐于此地。共享太平之烟月者。亦莫非 圣主之恩泽也。愿吾宗诸君子。各自敕励。更相劝勉。念众枝同根之道。奉先思孝。体生三如一之义。事上以忠。为祖先之肖孙。为圣上之荩臣。以永令名。岂不美哉。咸日唯唯。敢不服
昭穆有序。祭毕将修谱。以村舍狭隘。并辔向寺门西行十馀里。由东城而入。达于所谓天柱寺者。寺藏城西最高峰下。城中凡有九寺。而坐地眼界此为最云。团圆一堂。接膝连袂。乃取前印之谱本。更记后孙之名字。以为增刊广传之地。而沽取松醪。各倾数杯。舒古情之绸缪。吐新语之阑珊。于时积雨初收。霁景方明。相与联翩步陟寺后峰。登所谓上将台。四面轩豁。无所障碍。远近江山。总入眼底。前临粉堞。尚记古国之城郭。(此地即百济始祖温祚古城。)俯瞰沙场。缅忆忠魂之愤郁。遂皆徘徊散步。慷慨悲吟。龙城崔是翁。乃抚釰雪涕。中坐而言曰行宫枕戈。呜呼前王不忘。含香执靮。忍想先子遗踪。(我祖考丙子。以左承旨扈 驾。故 赐祭文。有执靮捍王等语。)山川不改。人事易变。当时事迹。恍如昨日。而屈指于今。奄成七十二年矣。嗟夫士生天地间。忠与孝而已。非忠无君。非孝无亲。今吾侪得保旧业之青毡。能守世传之素节者。莫非吾祖先之德荫也。优游以乐于此地。共享太平之烟月者。亦莫非 圣主之恩泽也。愿吾宗诸君子。各自敕励。更相劝勉。念众枝同根之道。奉先思孝。体生三如一之义。事上以忠。为祖先之肖孙。为圣上之荩臣。以永令名。岂不美哉。咸日唯唯。敢不服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6L 页
 膺。遂抽毫命楮。书以为崔氏宗会序。(丁亥十月)
膺。遂抽毫命楮。书以为崔氏宗会序。(丁亥十月)海山赠别序(宗兄天石寓居海美。又新卜于瑞山。故云海山。)
古人有言曰民吾同胞。况在同宗之人乎。又况袒免之亲乎。念我诸兄弟。同是太史三溪公出也。当初一人之身。而今成十寸之远。此则所谓势之无奈何者。祗是在我之情义。岂可不思所以自尽之道乎。第恨南北胥远。道路相左。吊庆不即时闻。休戚未能与同。悠悠日月之间。每切悬悬之念。乃者委涉千里之险途。幸做一场之好会。弟兄毕至。尽怡愉之道。叔侄咸集。纾绸缪之情。论今而考古。讲诗而说礼。不觉迟日之累改。都忘世故之多端。此亦浮生一难得底事也。今当作别。杳无前期。掺手临歧。黯然销魂。玆将一言。以为他日不忘之资云尔。(壬申)
送金子厚(万裁)归京序(甲戌四月。 中殿复位。金君被放送。饯于三溪。)
夫物受变而后成其材。人涉难而后益其智。是以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盖不如是。则无以熟人之仁而全人之德矣。今君以大贤之孙。袭世阀之烈。学可以承其家。才可以传其业也。犹未免困于憸小之手。厄于迁谪之间。心志之苦甚矣。体肤之饿极矣。岂非所谓拂乱其所为而将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7H 页
 降大任者耶。玆者太阳中天。群阴并息。深山穷谷之中。亦皆有和煦敷荣之气像。金鸡行色。返向京华。将见收拾民情。辅翼王猷。伸于久屈之馀。而用于至足之后。岂非所谓德全仁熟而能成才者耶。然则天之玉汝于君者。顾不大欤。虽然满盈之物。持之实难。渊冰之戒。人所易忽。更愿察循环之理。念苞桑之戒。安不忘危。忿必思难。自警于身。又勖诸弟。益坚素履。善守青毡。趾前美而裕后谟也。如我不文不武。无用于世。匏系穷巷。不求闻知。缘君行吟泽畔。时以相从于寂寞之滨。君今去矣。不能无怅然于怀。玆将一言。贺君之成其才。而道吾之惜其别也。
降大任者耶。玆者太阳中天。群阴并息。深山穷谷之中。亦皆有和煦敷荣之气像。金鸡行色。返向京华。将见收拾民情。辅翼王猷。伸于久屈之馀。而用于至足之后。岂非所谓德全仁熟而能成才者耶。然则天之玉汝于君者。顾不大欤。虽然满盈之物。持之实难。渊冰之戒。人所易忽。更愿察循环之理。念苞桑之戒。安不忘危。忿必思难。自警于身。又勖诸弟。益坚素履。善守青毡。趾前美而裕后谟也。如我不文不武。无用于世。匏系穷巷。不求闻知。缘君行吟泽畔。时以相从于寂寞之滨。君今去矣。不能无怅然于怀。玆将一言。贺君之成其才。而道吾之惜其别也。山西杂录后序
山西杂录者。故进士赵公庆男善述之所作。山西其号也。其先汉阳人。判中枢惠之后。户曹判书崇进之玄孙也。其考司直璧娶于南原梁氏。因居于府东元川里。以 隆庆庚午生公。天赋颖悟。才能学语。已诵花笑槛前月到天心等句。司直喜其奇俊。抚爱特甚。乙亥司直殁。公在姆背。悲不自胜。见者为之感动。七岁始入学。一闻辄诵。己卯秋。就傅于柳上舍仁沃。始有制述。而语辄惊人。上舍大加奖许。读书之暇。揉木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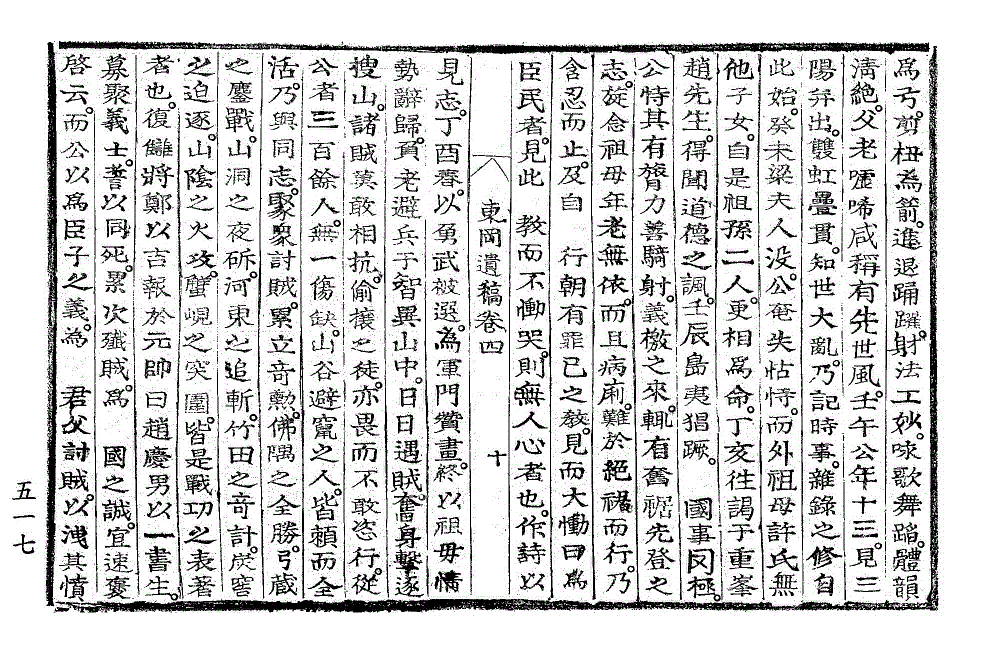 为弓。剪杻为箭。进退踊跃。射法工妙。咏歌舞蹈。体韵清绝。父老嘘唏咸称有先世风。壬午公年十三。见三阳并出。双虹叠贯。知世大乱。乃记时事。杂录之修自此始。癸未梁夫人没。公奄失怙恃。而外祖母许氏无他子女。自是祖孙二人。更相为命。丁亥往谒于重峰赵先生。得闻道德之讽。壬辰岛夷猖蹶。 国事罔极。公恃其有膂力善骑射。义檄之来。辄有奋裾先登之志。旋念祖母年老无依。而且病𢈱。难于绝裾而行。乃含忍而止。及自 行朝有罪已之教。见而大恸曰为臣民者。见此 教而不恸哭。则无人心者也。作诗以见志。丁酉春。以勇武被选。为军门赞画。终以祖母情势辞归。负老避兵于智异山中。日日遇贼。奋身击逐搜山。诸贼莫敢相抗。偷攘之徒。亦畏而不敢恣行。从公者三百馀人。无一伤缺。山谷避窜之人。皆赖而全活。乃与同志。聚众讨贼。累立奇勋。佛隅之全胜。弓藏之鏖战。山洞之夜斫。河东之追斩。竹田之奇计。炭窖之迫逐。山阴之火攻。蟹岘之突围。皆是战功之表著者也。复雠将郑以吉报于元帅曰赵庆男以一书生。募聚义士。誓以同死。累次歼贼。为 国之诚。宜速褒启云。而公以为臣子之义。为 君父讨贼。以泄其愤
为弓。剪杻为箭。进退踊跃。射法工妙。咏歌舞蹈。体韵清绝。父老嘘唏咸称有先世风。壬午公年十三。见三阳并出。双虹叠贯。知世大乱。乃记时事。杂录之修自此始。癸未梁夫人没。公奄失怙恃。而外祖母许氏无他子女。自是祖孙二人。更相为命。丁亥往谒于重峰赵先生。得闻道德之讽。壬辰岛夷猖蹶。 国事罔极。公恃其有膂力善骑射。义檄之来。辄有奋裾先登之志。旋念祖母年老无依。而且病𢈱。难于绝裾而行。乃含忍而止。及自 行朝有罪已之教。见而大恸曰为臣民者。见此 教而不恸哭。则无人心者也。作诗以见志。丁酉春。以勇武被选。为军门赞画。终以祖母情势辞归。负老避兵于智异山中。日日遇贼。奋身击逐搜山。诸贼莫敢相抗。偷攘之徒。亦畏而不敢恣行。从公者三百馀人。无一伤缺。山谷避窜之人。皆赖而全活。乃与同志。聚众讨贼。累立奇勋。佛隅之全胜。弓藏之鏖战。山洞之夜斫。河东之追斩。竹田之奇计。炭窖之迫逐。山阴之火攻。蟹岘之突围。皆是战功之表著者也。复雠将郑以吉报于元帅曰赵庆男以一书生。募聚义士。誓以同死。累次歼贼。为 国之诚。宜速褒启云。而公以为臣子之义。为 君父讨贼。以泄其愤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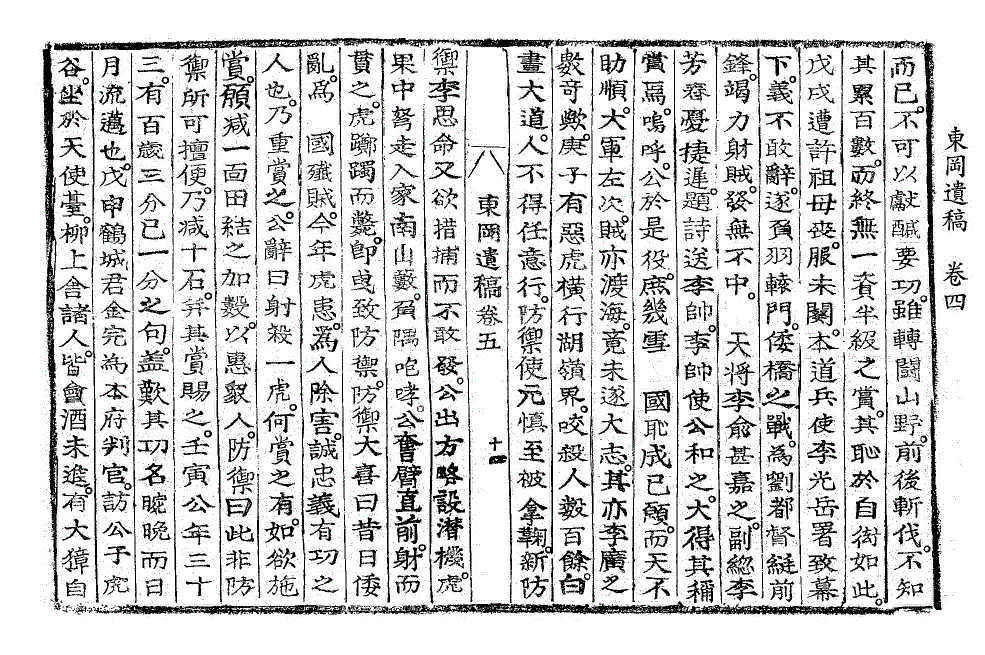 而已。不可以献咸要功。虽转斗山野。前后斩伐。不知其累百数。而终无一资半级之赏。其耻于自衒如此。戊戌遭许祖母丧。服未阕。本道兵使李光岳署致幕下。义不敢辞。遂负羽辕门。倭桥之战。为刘都督綎前锋。竭力射贼。发无不中。 天将李俞甚嘉之。副总李芳春忧捷迟。题诗送李帅。李帅使公和之。大得其称赏焉。呜呼。公于是役。庶几雪 国耻成己愿。而天不助顺。大军左次。贼亦渡海。竟未遂大志。其亦李广之数奇欤。庚子有恶虎横行湖岭界。咬杀人数百馀。白昼大道。人不得任意行。防御使元慎至被拿鞠。新防御李思命又欲措捕而不敢发。公出方略设潜机。虎果中弩走入家南山薮。负隅咆哮。公奋臂直前。射而贯之。虎踯躅而毙。即曳致防御。防御大喜曰昔日倭乱。为 国歼贼。今年虎患。为人除害。诚忠义有功之人也。乃重赏之。公辞曰射杀一虎。何赏之有。如欲施赏。愿减一面田结之加数。以惠众人。防御曰此非防御所可擅便。乃减十石。并其赏赐之。壬寅公年三十三。有百岁三分已一分之句。盖叹其功名晼晚而日月流迈也。戊申鹤城君金完为本府判官。访公于虎谷。坐于天使台。柳上舍诸人。皆会酒未进。有大獐自
而已。不可以献咸要功。虽转斗山野。前后斩伐。不知其累百数。而终无一资半级之赏。其耻于自衒如此。戊戌遭许祖母丧。服未阕。本道兵使李光岳署致幕下。义不敢辞。遂负羽辕门。倭桥之战。为刘都督綎前锋。竭力射贼。发无不中。 天将李俞甚嘉之。副总李芳春忧捷迟。题诗送李帅。李帅使公和之。大得其称赏焉。呜呼。公于是役。庶几雪 国耻成己愿。而天不助顺。大军左次。贼亦渡海。竟未遂大志。其亦李广之数奇欤。庚子有恶虎横行湖岭界。咬杀人数百馀。白昼大道。人不得任意行。防御使元慎至被拿鞠。新防御李思命又欲措捕而不敢发。公出方略设潜机。虎果中弩走入家南山薮。负隅咆哮。公奋臂直前。射而贯之。虎踯躅而毙。即曳致防御。防御大喜曰昔日倭乱。为 国歼贼。今年虎患。为人除害。诚忠义有功之人也。乃重赏之。公辞曰射杀一虎。何赏之有。如欲施赏。愿减一面田结之加数。以惠众人。防御曰此非防御所可擅便。乃减十石。并其赏赐之。壬寅公年三十三。有百岁三分已一分之句。盖叹其功名晼晚而日月流迈也。戊申鹤城君金完为本府判官。访公于虎谷。坐于天使台。柳上舍诸人。皆会酒未进。有大獐自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8L 页
 长法山。下于稻田。鹤城曰可惜赵兄老矣。若获此獐。可代苏仙之赤壁得鱼。公即把罗将棍。下台搜逐不及五六十步。獐入掌握。生致台上。鹤城大喜。贺其不衰。府伯成令公安义叹曰吾以某只谓文章巨擘。岂料其有此逐兽之勇。昨日之獐。不啻文万户之虎也。己酉中乡解两场。屈于礼部。丁巳又贯三场。时李许当国。见其政乱伦丧。遂废举杜门。扁其堂曰昼梦。惟以书籍自娱。癸亥天佑大东。 仁祖改玉。士林之深藏不市者。皆弹冠而出。公亦应举。登甲子进士。自是屏迹衡门。绝意世事。遂筑别业于方丈山西龙湫洞里。徜徉逍遥。自称山西病翁。噫。公以英拔嵬伟之资。有忠孝慷慨之节。龙蛇之变。忧国愤贼。扼腕流涕。只以祖母日迫西山。不得许身于国。而犹能奋义杀贼。其所素蓄积。槩可想矣。李忠悯以统制立大功。而中丸卒。公诗以悼之。逮至丙丁。则衰病已甚。望断赴难。而徒切忠愤。闻三学士殉节沈中。感慨作诗曰杀身柴市文承相。饿死燕京谢信州。其忠义之气。老而不衰者。又可见矣。在舞勺之年。仰观日变。逆知时乱。随其见闻。有此集成。童年先见。尤可奇也。自壬午止于戊寅。乃以五十七年间事。为巨编八帙之书。名曰山
长法山。下于稻田。鹤城曰可惜赵兄老矣。若获此獐。可代苏仙之赤壁得鱼。公即把罗将棍。下台搜逐不及五六十步。獐入掌握。生致台上。鹤城大喜。贺其不衰。府伯成令公安义叹曰吾以某只谓文章巨擘。岂料其有此逐兽之勇。昨日之獐。不啻文万户之虎也。己酉中乡解两场。屈于礼部。丁巳又贯三场。时李许当国。见其政乱伦丧。遂废举杜门。扁其堂曰昼梦。惟以书籍自娱。癸亥天佑大东。 仁祖改玉。士林之深藏不市者。皆弹冠而出。公亦应举。登甲子进士。自是屏迹衡门。绝意世事。遂筑别业于方丈山西龙湫洞里。徜徉逍遥。自称山西病翁。噫。公以英拔嵬伟之资。有忠孝慷慨之节。龙蛇之变。忧国愤贼。扼腕流涕。只以祖母日迫西山。不得许身于国。而犹能奋义杀贼。其所素蓄积。槩可想矣。李忠悯以统制立大功。而中丸卒。公诗以悼之。逮至丙丁。则衰病已甚。望断赴难。而徒切忠愤。闻三学士殉节沈中。感慨作诗曰杀身柴市文承相。饿死燕京谢信州。其忠义之气。老而不衰者。又可见矣。在舞勺之年。仰观日变。逆知时乱。随其见闻。有此集成。童年先见。尤可奇也。自壬午止于戊寅。乃以五十七年间事。为巨编八帙之书。名曰山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9H 页
 西杂录。其于朝廷之事变。民生之休戚。时运之盛衰。世道之污隆。无不备载。而严于淑慝逆顺之分。尤惓惓于忠臣节士之迹。能使善者有所劝。恶者有所惧。实是衰世之一龟鉴也。有关于世道者亦大矣。公以名家遗裔。流落南乡。不幸早孤。而乃能自奋力学。文章足以鸣于世。智勇足以显于时。而才命不谋。赍志以殁。良可惜也。呜呼。公虽不遇于当时。惟玆一书。可以有传于后世。虽谓之不朽可也。记昔甲子岁。公之折莲而到门也。吾先子判书公时以掌令。见邀于庆席。今公所抱秀才愃甫。袖其书来示余。求所以发挥者。余今年八十有一。衰病杜门。无意于翰墨。而念及畴曩。不胜感怀。不敢以老拙孤其意。乃取公自叙。略加删定。间附所传闻于前辈者。以为一通。而至其当日人谋之臧否。事势之缓急。观此集者。自可以知之。今不复覼缕焉。
西杂录。其于朝廷之事变。民生之休戚。时运之盛衰。世道之污隆。无不备载。而严于淑慝逆顺之分。尤惓惓于忠臣节士之迹。能使善者有所劝。恶者有所惧。实是衰世之一龟鉴也。有关于世道者亦大矣。公以名家遗裔。流落南乡。不幸早孤。而乃能自奋力学。文章足以鸣于世。智勇足以显于时。而才命不谋。赍志以殁。良可惜也。呜呼。公虽不遇于当时。惟玆一书。可以有传于后世。虽谓之不朽可也。记昔甲子岁。公之折莲而到门也。吾先子判书公时以掌令。见邀于庆席。今公所抱秀才愃甫。袖其书来示余。求所以发挥者。余今年八十有一。衰病杜门。无意于翰墨。而念及畴曩。不胜感怀。不敢以老拙孤其意。乃取公自叙。略加删定。间附所传闻于前辈者。以为一通。而至其当日人谋之臧否。事势之缓急。观此集者。自可以知之。今不复覼缕焉。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记
复学斋记
南原即带方古国也。人物之殷富。甲于湖南。山川之奇丽。鸣于海东。是以 国家常选用重人为倅宰。今太守李公显章。 璿源宝系。金闺雅望。早折蟾宫之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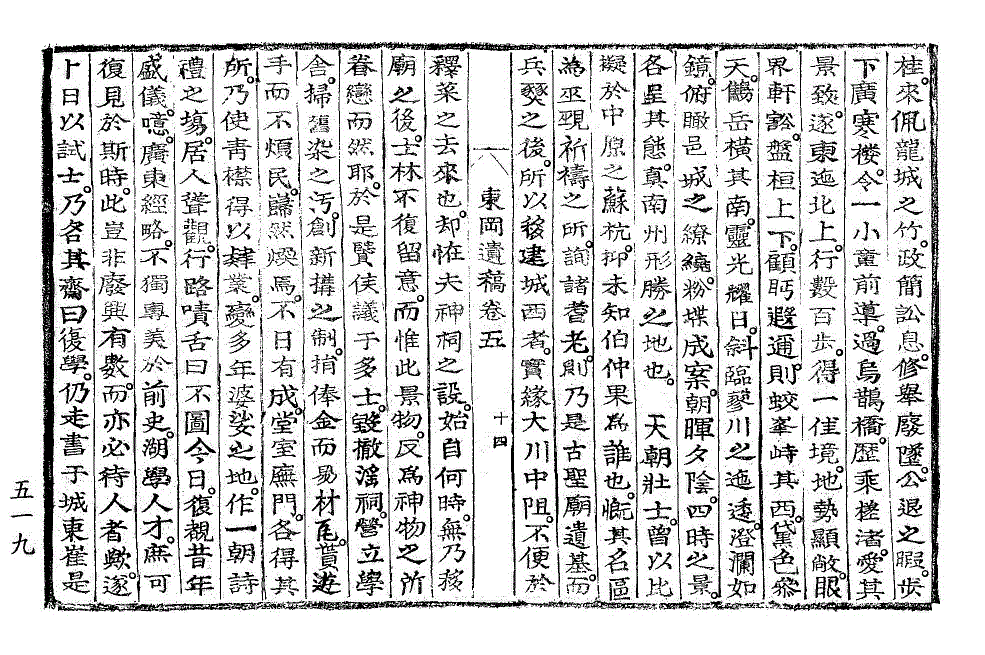 桂。来佩龙城之竹。政简讼息。修举废坠。公退之暇。步下广寒楼。令一小童前导。过乌鹊桥。历乘槎渚。爱其景致。遂东迤北上。行数百步。得一佳境。地势显敞。眼界轩豁。盘桓上下。顾眄遐迩。则蛟峰峙其西。黛色参天。鹪岳横其南。灵光耀日。斜临蓼川之迤逶。澄澜如镜。俯瞰邑城之缭绕。粉堞成案。朝晖夕阴。四时之景。各呈其态。真南州形胜之地也。 天朝壮士。曾以比拟于中原之苏杭。抑未知伯仲果为谁也。慨其名区为巫觋祈祷之所。询诸耆老。则乃是古圣庙遗基。而兵燹之后。所以移建城西者。实缘大川中阻。不便于释菜之去来也。却怪夫神祠之设。始自何时。无乃移庙之后。士林不复留意。而惟此景物。反为神物之所眷恋而然耶。于是贤侯议于多士。毁撤淫祠。营立学舍。扫旧染之污。创新搆之制。捐俸金而易材瓦。贳游手而不烦民。岿然焕焉。不日有成。堂室庑门。各得其所。乃使青襟得以肄业。变多年婆娑之地。作一朝诗礼之场。居人耸观。行路啧舌曰不图今日。复睹昔年盛仪。噫。广东经略。不独专美于前史。湖学人才。庶可复见于斯时。此岂非废兴有数。而亦必待人者欤。遂卜日以试士。乃名其斋曰复学。仍走书于城东崔是
桂。来佩龙城之竹。政简讼息。修举废坠。公退之暇。步下广寒楼。令一小童前导。过乌鹊桥。历乘槎渚。爱其景致。遂东迤北上。行数百步。得一佳境。地势显敞。眼界轩豁。盘桓上下。顾眄遐迩。则蛟峰峙其西。黛色参天。鹪岳横其南。灵光耀日。斜临蓼川之迤逶。澄澜如镜。俯瞰邑城之缭绕。粉堞成案。朝晖夕阴。四时之景。各呈其态。真南州形胜之地也。 天朝壮士。曾以比拟于中原之苏杭。抑未知伯仲果为谁也。慨其名区为巫觋祈祷之所。询诸耆老。则乃是古圣庙遗基。而兵燹之后。所以移建城西者。实缘大川中阻。不便于释菜之去来也。却怪夫神祠之设。始自何时。无乃移庙之后。士林不复留意。而惟此景物。反为神物之所眷恋而然耶。于是贤侯议于多士。毁撤淫祠。营立学舍。扫旧染之污。创新搆之制。捐俸金而易材瓦。贳游手而不烦民。岿然焕焉。不日有成。堂室庑门。各得其所。乃使青襟得以肄业。变多年婆娑之地。作一朝诗礼之场。居人耸观。行路啧舌曰不图今日。复睹昔年盛仪。噫。广东经略。不独专美于前史。湖学人才。庶可复见于斯时。此岂非废兴有数。而亦必待人者欤。遂卜日以试士。乃名其斋曰复学。仍走书于城东崔是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0H 页
 翁。俾记其事。辞以老不得。略叙其颠末如右云。
翁。俾记其事。辞以老不得。略叙其颠末如右云。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跋
太虚亭文集重刊跋
我先祖太虚亭文集凡若干卷。四佳徐先生实会稡而弁其首。刊行于世久矣。不幸壬丙兵燹之馀。梓本无存。藏书者绝无。顷岁玉堂儒臣启于 朝。求诸远迩。南原小宗舍伯家。有世传印本一秩。自本府缮写以上之。未获剞劂之便。常用慨然。去年秋。舍弟启翁除得灵光郡事。为谢 命入京师。适遇宗叔鼎铉氏新授全罗右水伯。合谋所以广其传者。启翁未及 陛辞。旋移入侍讲院。宗叔乃专掌其事。训鍊戎兵之暇。拮据工匠之役。不数月而就绪。其亦勤矣。仍以书来。俾记其事实。是翁窃念我先祖文章事业。载在 国乘。前辈于序文碑志。亦已槩论之。今不敢复赘一辞。第此板本之前后成毁。必待言而后可知也。且卷末二篇。即先君鳌洲公考诸他书。誊留旧本之所无者。乃今添录而目之以补遗。张头所表。是从祖砭斋公质之他本。拈出文义之可疑者。今又誊刻而并录其识文。故略叙其始末如右焉。呜呼。公之没二百有三十有四载矣。今读遗文。尚使人兴喟。况我云仍辈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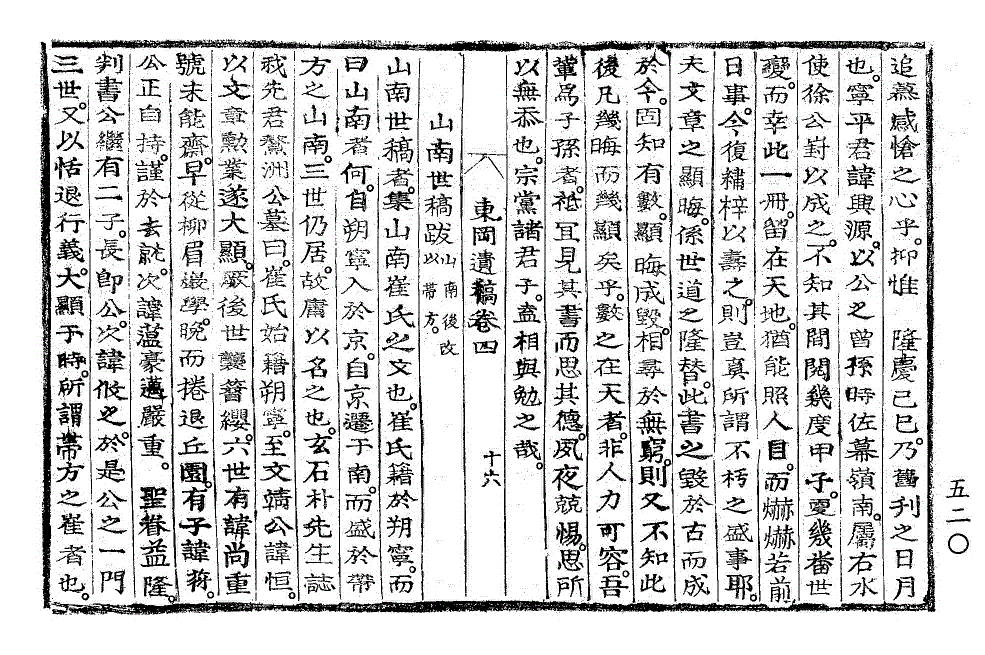 追慕感怆之心乎。抑惟 隆庆己巳。乃旧刊之日月也。宁平君讳兴源。以公之曾孙时佐幕岭南。属右水使徐公崶以成之。不知其间阅几度甲子。更几番世变。而幸此一册。留在天地。犹能照人目。而赫赫若前日事。今复绣梓以寿之。则岂真所谓不朽之盛事耶。夫文章之显晦。系世道之隆替。此书之毁于古而成于今。固知有数。显晦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又不知此后凡几晦而几显矣乎。数之在天者。非人力可容。吾辈为子孙者。祗宜见其书而思其德。夙夜兢惕。思所以无忝也。宗党诸君子。盍相与勉之哉。
追慕感怆之心乎。抑惟 隆庆己巳。乃旧刊之日月也。宁平君讳兴源。以公之曾孙时佐幕岭南。属右水使徐公崶以成之。不知其间阅几度甲子。更几番世变。而幸此一册。留在天地。犹能照人目。而赫赫若前日事。今复绣梓以寿之。则岂真所谓不朽之盛事耶。夫文章之显晦。系世道之隆替。此书之毁于古而成于今。固知有数。显晦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又不知此后凡几晦而几显矣乎。数之在天者。非人力可容。吾辈为子孙者。祗宜见其书而思其德。夙夜兢惕。思所以无忝也。宗党诸君子。盍相与勉之哉。山南世稿跋(山南后改以带方。)
山南世稿者。集山南崔氏之文也。崔氏籍于朔宁。而曰山南者何。自朔宁入于京。自京迁于南。而盛于带方之山南。三世仍居。故庸以名之也。玄石朴先生志我先君鳌洲公墓曰。崔氏始籍朔宁。至文靖公讳恒。以文章勋业遂大显。厥后世袭簪缨。六世有讳尚重号未能斋。早从柳眉岩学。晚而捲退丘园。有子讳莚。公正自持。谨于去就。次讳蕴豪迈严重。 圣眷益隆。判书公继有二子。长即公。次讳攸之。于是公之一门三世。又以恬退行义。大显于时。所谓带方之崔者也。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1H 页
 噫。此乃古人述家风陈世德之意也。念惟先生养德林泉。为士林所宗仰。当时求不朽之文者。无论韦布搢绅。皆走于其门。第先生沉重简默。于人少许可。必泾渭于心胸之间。而权衡于论说之际。故得其文者或寡矣。独我一门三世见许乃如此。则是实公论也。我三世文集。宜有以早见于世。而我先子尝言吾东方文集之太烦。实为时弊。是故虽以文靖公之文章勋业。其文之行于世者。不过太虚亭集二卷而已也。其后言论事迹。岂无可见者。而不但中间为丙丁兵燹之所灾。实缘戒其以文而招尤速祸。贵其无名而含光混世也。然非文则后世无所考。子孙无所法。或近于因噎而废食矣。玆乃近取未能斋以下三世文字之可考者若干篇。合成一帙。名之曰山南世稿凡五卷。初卷一篇。未能斋遗稿也。第二第三。则星湾,砭斋二公遗文各一篇也。四卷五卷。乃鳌洲,艮湖二公之文亦各一篇也。呜呼。文者贯道之器。而诗又发于性情者也。见一斑而知全豹。则顾何必多乎哉。谨依儒宗所论一门三世之言。不敢更有加焉。又删其冗就其约。上以体祖先太烦之戒。下以启子孙肯搆之资云。
噫。此乃古人述家风陈世德之意也。念惟先生养德林泉。为士林所宗仰。当时求不朽之文者。无论韦布搢绅。皆走于其门。第先生沉重简默。于人少许可。必泾渭于心胸之间。而权衡于论说之际。故得其文者或寡矣。独我一门三世见许乃如此。则是实公论也。我三世文集。宜有以早见于世。而我先子尝言吾东方文集之太烦。实为时弊。是故虽以文靖公之文章勋业。其文之行于世者。不过太虚亭集二卷而已也。其后言论事迹。岂无可见者。而不但中间为丙丁兵燹之所灾。实缘戒其以文而招尤速祸。贵其无名而含光混世也。然非文则后世无所考。子孙无所法。或近于因噎而废食矣。玆乃近取未能斋以下三世文字之可考者若干篇。合成一帙。名之曰山南世稿凡五卷。初卷一篇。未能斋遗稿也。第二第三。则星湾,砭斋二公遗文各一篇也。四卷五卷。乃鳌洲,艮湖二公之文亦各一篇也。呜呼。文者贯道之器。而诗又发于性情者也。见一斑而知全豹。则顾何必多乎哉。谨依儒宗所论一门三世之言。不敢更有加焉。又删其冗就其约。上以体祖先太烦之戒。下以启子孙肯搆之资云。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赞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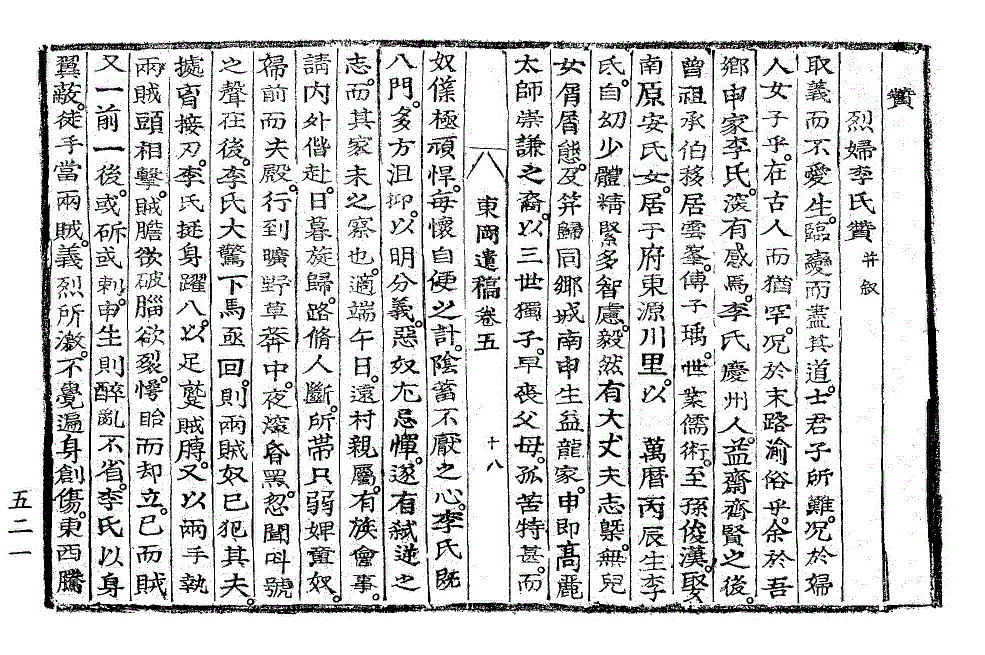 烈妇李氏赞(并叙)
烈妇李氏赞(并叙)取义而不爱生。临变而尽其道。士君子所难。况于妇人女子乎。在古人而犹罕。况于末路渝俗乎。余于吾乡申家李氏。深有感焉。李氏庆州人。益斋齐贤之后。曾祖承伯移居云峰。传子瑀。世业儒术。至孙俊汉。娶南原安氏女。居于府东源川里。以 万历丙辰生李氏。自幼少体精紧多智虑。毅然有大丈夫志槩。无儿女屑屑态。及笄归同乡城南申生益龙家。申即高丽太师崇谦之裔。以三世独子。早丧父母。孤苦特甚。而奴仆极顽悍。每怀自便之计。阴蓄不厌之心。李氏既入门。多方沮抑。以明分义。恶奴尤忌惮。遂有弑逆之志。而其家未之察也。适端午日。远村亲属。有族会事。请内外偕赴。日暮旋归。路脩人断。所带只弱婢童奴。妇前而夫殿。行到旷野草莽中。夜深昏黑。忽闻叫号之声在后。李氏大惊下马亟回。则两贼奴已犯其夫。据胸接刃。李氏挺身跃入。以足蹴贼膞。又以两手执两贼头相击。贼胆欲破脑欲裂。愕眙而却立。已而贼又一前一后。或斫或刺。申生则醉乱不省。李氏以身翼蔽。徒手当两贼。义烈所激。不觉遍身创伤。东西腾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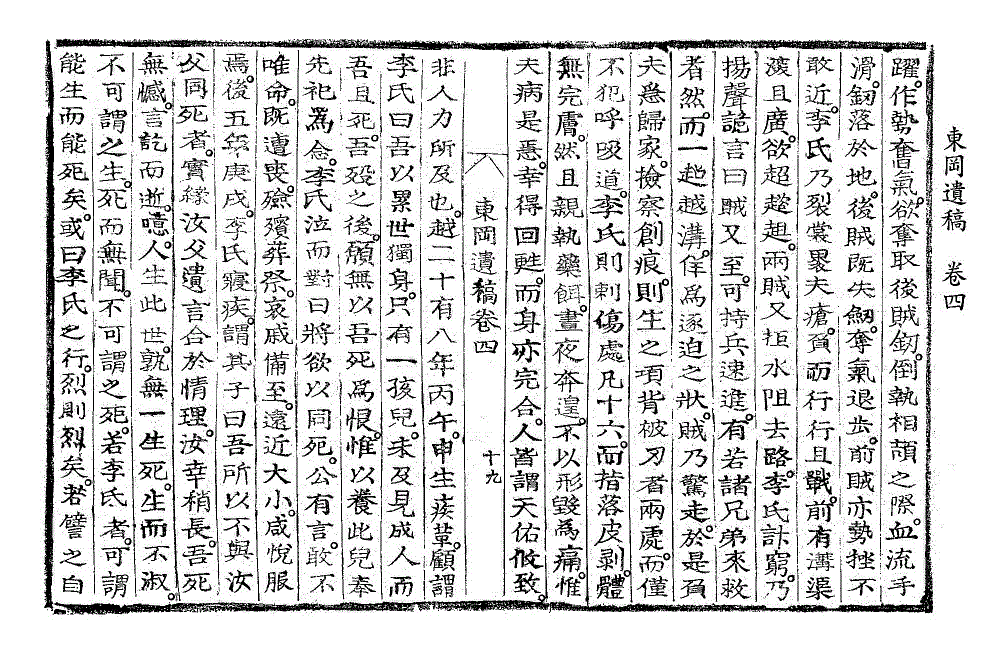 跃。作势奋气。欲夺取后贼釰。倒执相颉之际。血流手滑。釰落于地。后贼既失剑。夺气退步。前贼亦势挫不敢近。李氏乃裂裳裹夫疮。负而行行且战。前有沟渠深且广。欲超趑趄。两贼又拒水阻去路。李氏计穷。乃扬声诡言曰贼又至。可持兵速进。有若诸兄弟来救者然。而一超越沟。佯为逐迫之状。贼乃惊走。于是负夫急归家。捡察创痕。则生之项背被刃者两处。而仅不犯呼吸道。李氏则刺伤处凡十六。而指落皮剥。体无完肤。然且亲执药饵。昼夜奔遑。不以形毁为痛。惟夫病是急。幸得回苏。而身亦完合。人皆谓天佑攸致。非人力所及也。越二十有八年丙午。申生疾革。顾谓李氏曰吾以累世独身。只有一孩儿。未及见成人而吾且死。吾殁之后。愿无以吾死为恨。惟以养此儿奉先祀为念。李氏泣而对曰将欲以同死。公有言。敢不唯命。既遭丧。殓殡葬祭。哀戚备至。远近大小。咸悦服焉。后五年庚戌。李氏寝疾。谓其子曰吾所以不与汝父同死者。实缘汝父遗言合于情理。汝幸稍长。吾死无憾。言讫而逝。噫。人生此世。孰无一生死。生而不淑。不可谓之生。死而无闻。不可谓之死。若李氏者。可谓能生而能死矣。或曰李氏之行。烈则烈矣。若譬之自
跃。作势奋气。欲夺取后贼釰。倒执相颉之际。血流手滑。釰落于地。后贼既失剑。夺气退步。前贼亦势挫不敢近。李氏乃裂裳裹夫疮。负而行行且战。前有沟渠深且广。欲超趑趄。两贼又拒水阻去路。李氏计穷。乃扬声诡言曰贼又至。可持兵速进。有若诸兄弟来救者然。而一超越沟。佯为逐迫之状。贼乃惊走。于是负夫急归家。捡察创痕。则生之项背被刃者两处。而仅不犯呼吸道。李氏则刺伤处凡十六。而指落皮剥。体无完肤。然且亲执药饵。昼夜奔遑。不以形毁为痛。惟夫病是急。幸得回苏。而身亦完合。人皆谓天佑攸致。非人力所及也。越二十有八年丙午。申生疾革。顾谓李氏曰吾以累世独身。只有一孩儿。未及见成人而吾且死。吾殁之后。愿无以吾死为恨。惟以养此儿奉先祀为念。李氏泣而对曰将欲以同死。公有言。敢不唯命。既遭丧。殓殡葬祭。哀戚备至。远近大小。咸悦服焉。后五年庚戌。李氏寝疾。谓其子曰吾所以不与汝父同死者。实缘汝父遗言合于情理。汝幸稍长。吾死无憾。言讫而逝。噫。人生此世。孰无一生死。生而不淑。不可谓之生。死而无闻。不可谓之死。若李氏者。可谓能生而能死矣。或曰李氏之行。烈则烈矣。若譬之自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2L 页
 尽殉夫者。岂不犹有歉乎。余愀然曰此非知李氏本情而得论人之道者也。圣人有言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李氏之前所遭。乃蹈白刃之一节。匹妇为谅者。亦或可能也。后所处。乃庶几中庸。非褊浅妇人所可行也。或曰然则世之不与夫同死者。皆有是见。而自决下从者。又不必取欤。曰此不可以一槩论。只宜原其情而定褒贬也。如使李氏前无明白之行。后无可验其贞烈之情矣。前日之救夫。既出于忘死。则后日之不徇夫。非出于贪生也审矣。且其遭贼变也。合卺才四朔。而于归未阅月矣。已能忘生于未展眉之前。其肯惜死于亡所天之后乎。前则以夫为重。忘其身而救之。后则以奉先为重。从遗言而处之。其所取舍。岂不合于轻重之权乎。若不从其夫治命。随以同归。则嗣子不得长。而申氏遂绝不祀矣。岂可谓处变尽道乎。余故曰此士君子所难而古人之所罕也。余自少时。已闻其事而知其槩矣。及长接其同里士子。得详焉。尤服其义烈。今其子命锡从余游。以当时里任之论报。府伯之叹赏文迹来示。仍及其后来事。益信前闻之不差。自不觉起敬而兴喟也。嗟乎以李氏之烈行懿德。尚未蒙㫌淑表宅之典。岂徒乡邻之羞。
尽殉夫者。岂不犹有歉乎。余愀然曰此非知李氏本情而得论人之道者也。圣人有言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李氏之前所遭。乃蹈白刃之一节。匹妇为谅者。亦或可能也。后所处。乃庶几中庸。非褊浅妇人所可行也。或曰然则世之不与夫同死者。皆有是见。而自决下从者。又不必取欤。曰此不可以一槩论。只宜原其情而定褒贬也。如使李氏前无明白之行。后无可验其贞烈之情矣。前日之救夫。既出于忘死。则后日之不徇夫。非出于贪生也审矣。且其遭贼变也。合卺才四朔。而于归未阅月矣。已能忘生于未展眉之前。其肯惜死于亡所天之后乎。前则以夫为重。忘其身而救之。后则以奉先为重。从遗言而处之。其所取舍。岂不合于轻重之权乎。若不从其夫治命。随以同归。则嗣子不得长。而申氏遂绝不祀矣。岂可谓处变尽道乎。余故曰此士君子所难而古人之所罕也。余自少时。已闻其事而知其槩矣。及长接其同里士子。得详焉。尤服其义烈。今其子命锡从余游。以当时里任之论报。府伯之叹赏文迹来示。仍及其后来事。益信前闻之不差。自不觉起敬而兴喟也。嗟乎以李氏之烈行懿德。尚未蒙㫌淑表宅之典。岂徒乡邻之羞。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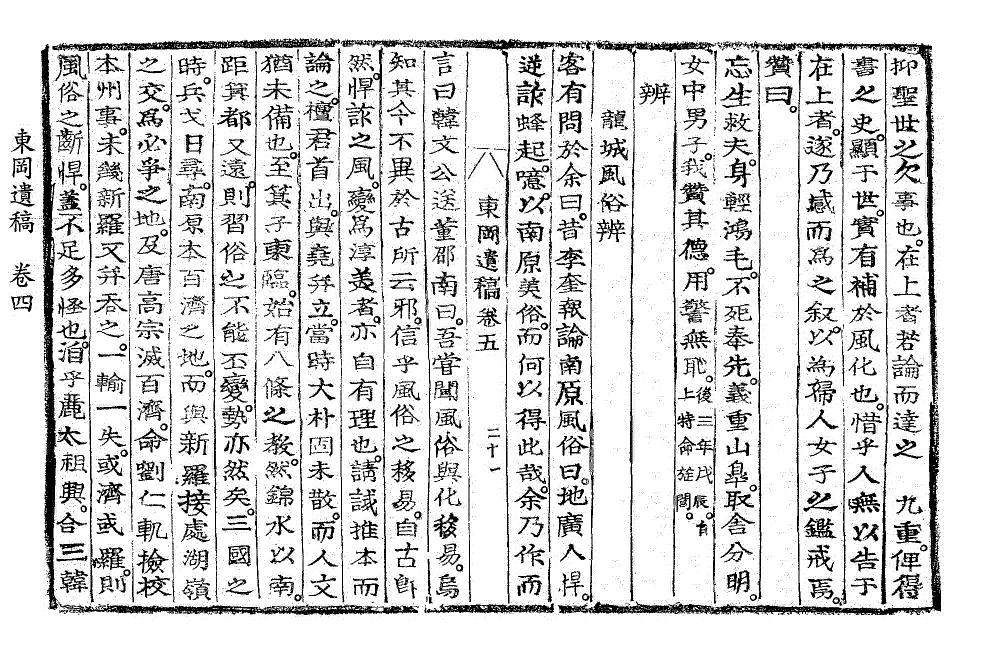 抑圣世之欠事也。在上者若论而达之 九重。俾得书之史。显于世。实有补于风化也。惜乎人无以告于在上者。遂乃感而为之叙。以为妇人女子之鉴戒焉。赞曰。
抑圣世之欠事也。在上者若论而达之 九重。俾得书之史。显于世。实有补于风化也。惜乎人无以告于在上者。遂乃感而为之叙。以为妇人女子之鉴戒焉。赞曰。忘生救夫。身轻鸿毛。不死奉先。义重山皋。取舍分明。女中男子。我赞其德。用警无耻。(后三年戊辰。自上特命㫌闾。)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辨
龙城风俗辨
客有问于余曰。昔李奎报论南原风俗曰。地广人悍。逆诈蜂起。噫。以南原美俗。而何以得此哉。余乃作而言曰韩文公送董邵南曰。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乌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信乎风俗之移易。自古即然。悍诈之风。变为淳美者。亦自有理也。请试推本而论之。檀君首出。与尧并立。当时大朴固未散。而人文犹未备也。至箕子东临。始有八条之教。然锦水以南。距箕都又远。则习俗之不能丕变。势亦然矣。三国之时。兵戈日寻。南原本百济之地。而与新罗接处湖岭之交。为必争之地。及唐高宗灭百济。命刘仁轨捡校本州事。未几新罗又并吞之。一输一失。或济或罗。则风俗之断悍。盖不足多怪也。洎乎丽太祖兴。合三韩
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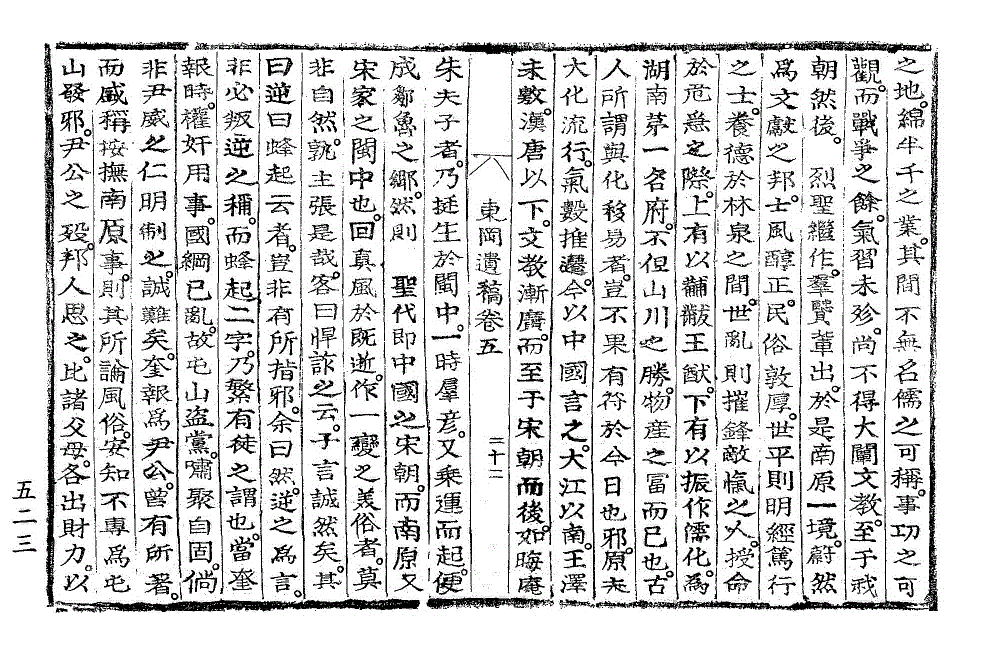 之地。绵半千之业。其间不无名儒之可称。事功之可观。而战争之馀。气习未殄。尚不得大阐文教。至于我朝然后。 烈圣继作。群贤辈出。于是南原一境。蔚然为文献之邦。士风醇正。民俗敦厚。世平则明经笃行之士。养德于林泉之间。世乱则摧锋敌忾之人。授命于危急之际。上有以黼黻王猷。下有以振作儒化。为湖南第一名府。不但山川之胜。物产之富而已也。古人所谓与化移易者。岂不果有符于今日也邪。原夫大化流行。气数推迁。今以中国言之。大江以南。王泽未敷。汉唐以下。文教渐广。而至于宋朝而后。如晦庵朱夫子者。乃挺生于闽中。一时群彦。又乘运而起。便成邹鲁之乡。然则 圣代即中国之宋朝。而南原又宋家之闽中也。回真风于既逝。作一变之美俗者。莫非自然。孰主张是哉。客曰悍诈之云。子言诚然矣。其曰逆曰蜂起云者。岂非有所指邪。余曰然。逆之为言。非必叛逆之称。而蜂起二字。乃繁有徒之谓也。当奎报时。权奸用事。国纲已乱。故屯山盗党。啸聚自固。倘非尹威之仁明制之。诚难矣。奎报为尹公。曾有所著。而盛称按抚南原事。则其所论风俗。安知不专为屯山发邪。尹公之殁。邦人思之。比诸父母。各出财力。以
之地。绵半千之业。其间不无名儒之可称。事功之可观。而战争之馀。气习未殄。尚不得大阐文教。至于我朝然后。 烈圣继作。群贤辈出。于是南原一境。蔚然为文献之邦。士风醇正。民俗敦厚。世平则明经笃行之士。养德于林泉之间。世乱则摧锋敌忾之人。授命于危急之际。上有以黼黻王猷。下有以振作儒化。为湖南第一名府。不但山川之胜。物产之富而已也。古人所谓与化移易者。岂不果有符于今日也邪。原夫大化流行。气数推迁。今以中国言之。大江以南。王泽未敷。汉唐以下。文教渐广。而至于宋朝而后。如晦庵朱夫子者。乃挺生于闽中。一时群彦。又乘运而起。便成邹鲁之乡。然则 圣代即中国之宋朝。而南原又宋家之闽中也。回真风于既逝。作一变之美俗者。莫非自然。孰主张是哉。客曰悍诈之云。子言诚然矣。其曰逆曰蜂起云者。岂非有所指邪。余曰然。逆之为言。非必叛逆之称。而蜂起二字。乃繁有徒之谓也。当奎报时。权奸用事。国纲已乱。故屯山盗党。啸聚自固。倘非尹威之仁明制之。诚难矣。奎报为尹公。曾有所著。而盛称按抚南原事。则其所论风俗。安知不专为屯山发邪。尹公之殁。邦人思之。比诸父母。各出财力。以东冈先生遗稿卷四 第 5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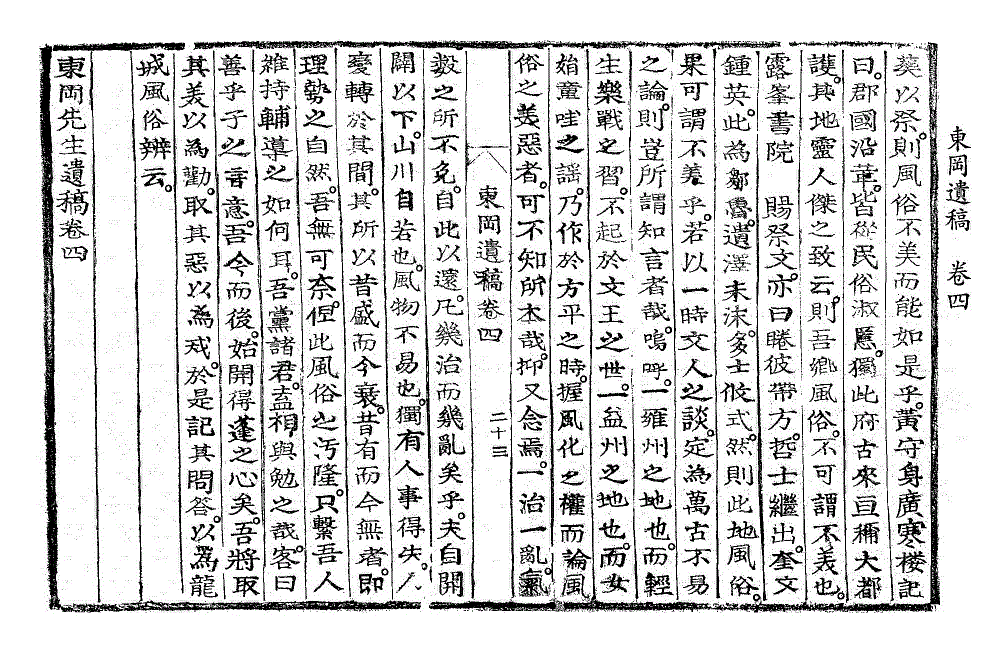 葬以祭。则风俗不美而能如是乎。黄守身广寒楼记曰。郡国沿革。皆从民俗淑慝。独此府古来亘称大都护。其地灵人杰之致云。则吾乡风俗。不可谓不美也。露峰书院 赐祭文。亦曰眷彼带方。哲士继出。奎文钟英。此为邹鲁。遗泽未沫。多士攸式。然则此地风俗。果可谓不美乎。若以一时文人之谈。定为万古不易之论。则岂所谓知言者哉。呜呼。一雍州之地也。而轻生乐战之习。不起于文王之世。一益州之地也。而女娟童哇之谣。乃作于方平之时。握风化之权而论风俗之美恶者。可不知所本哉。抑又念焉。一治一乱。气数之所不免。自此以还。凡几治而几乱矣乎。夫自开辟以下。山川自若也。风物不易也。独有人事得失。人变转于其间。其所以昔盛而今衰。昔有而今无者。即理势之自然。吾无可奈。但此风俗之污隆。只系吾人维持辅导之如何耳。吾党诸君。盍相与勉之哉。客曰善乎子之言意。吾今而后。始开得蓬之心矣。吾将取其美以为劝。取其恶以为戒。于是记其问答。以为龙城风俗辨云。
葬以祭。则风俗不美而能如是乎。黄守身广寒楼记曰。郡国沿革。皆从民俗淑慝。独此府古来亘称大都护。其地灵人杰之致云。则吾乡风俗。不可谓不美也。露峰书院 赐祭文。亦曰眷彼带方。哲士继出。奎文钟英。此为邹鲁。遗泽未沫。多士攸式。然则此地风俗。果可谓不美乎。若以一时文人之谈。定为万古不易之论。则岂所谓知言者哉。呜呼。一雍州之地也。而轻生乐战之习。不起于文王之世。一益州之地也。而女娟童哇之谣。乃作于方平之时。握风化之权而论风俗之美恶者。可不知所本哉。抑又念焉。一治一乱。气数之所不免。自此以还。凡几治而几乱矣乎。夫自开辟以下。山川自若也。风物不易也。独有人事得失。人变转于其间。其所以昔盛而今衰。昔有而今无者。即理势之自然。吾无可奈。但此风俗之污隆。只系吾人维持辅导之如何耳。吾党诸君。盍相与勉之哉。客曰善乎子之言意。吾今而后。始开得蓬之心矣。吾将取其美以为劝。取其恶以为戒。于是记其问答。以为龙城风俗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