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x 页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礼说○王朝礼
礼说○王朝礼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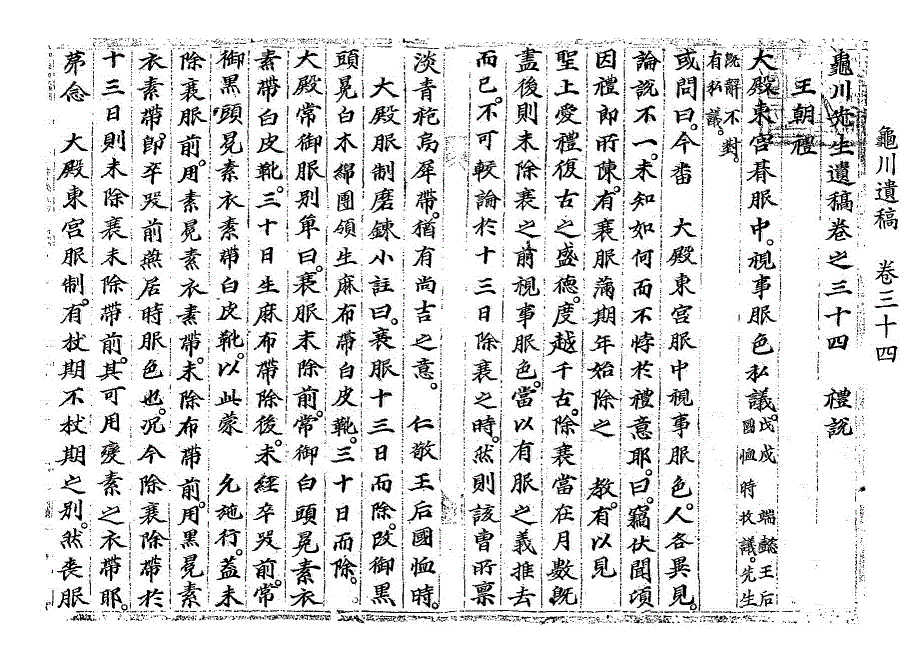 大殿东宫期服中。视事服色私议。(戊戌 端懿王后国恤时收议。先生既辞不对。有私议。)
大殿东宫期服中。视事服色私议。(戊戌 端懿王后国恤时收议。先生既辞不对。有私议。)或问曰。今番 大殿东宫服中视事服色。人各异见。论说不一。未知如何而不悖于礼意耶。曰。窃伏闻顷因礼郎所陈。有衰服满期年始除之 教。有以见 圣上爱礼复古之盛德。度越千古。除衰当在月数既尽后则未除衰之前视事服色。当以有服之义推去而已。不可较论于十三日除衰之时。然则该曹所禀淡青袍乌犀带。犹有尚吉之意。 仁敬王后国恤时。 大殿服制磨鍊小注曰。衰服十三日而除。改御黑头冕白木绵团领生麻布带白皮靴。三十日而除。 大殿常御服别单曰。衰服未除前。常御白头冕素衣素带白皮靴。三十日生麻布带除后。未经卒哭前。常御黑头冕素衣素带白皮靴。以此蒙 允施行。盖未除衰服前。用素冕素衣素带。未除布带前。用黑冕素衣素带。即卒哭前燕居时服色也。况今除衰除带于十三日则未除衰未除带前。其可用变素之衣带耶。第念 大殿东宫服制。有杖期不杖期之别。然丧服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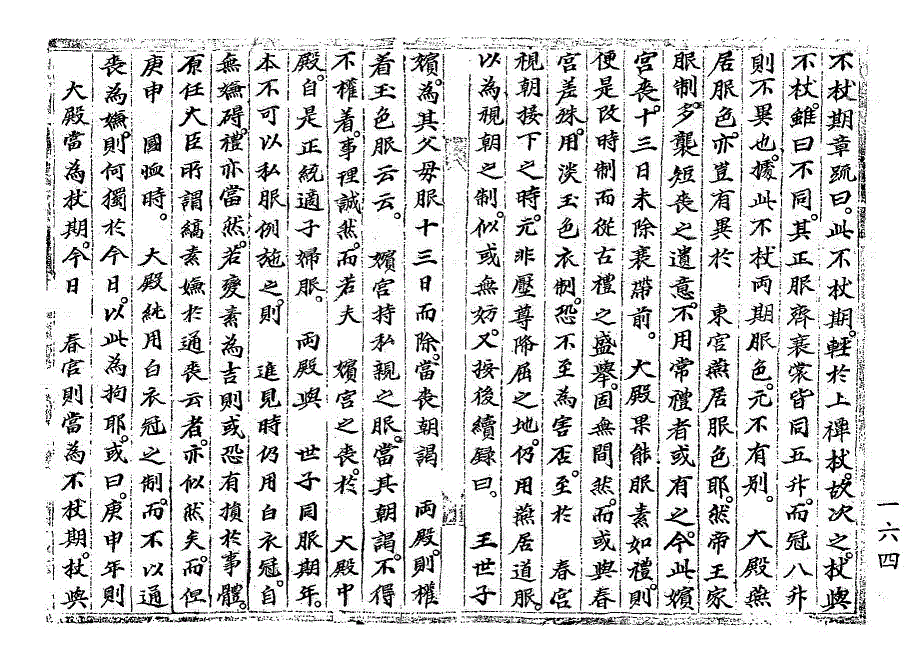 不杖期章疏曰。此不杖期。轻于上禫杖。故次之。杖与不杖。虽曰不同。其正服齐衰裳皆同五升。而冠八升则不异也。据此不杖两期服色。元不有别。 大殿燕居服色。亦岂有异于 东宫燕居服色耶。然帝王家服制。多袭短丧之遗意。不用常礼者或有之。今此嫔宫丧。十三日未除衰带前。 大殿果能服素如礼。则便是改时制而从古礼之盛举。固无间然。而或与春宫差殊。用淡玉色衣制。恐不至为害否。至于 春宫视朝接下之时。元非压尊降屈之地。仍用燕居道服。以为视朝之制。似或无妨。又按后续录曰。 王世子嫔。为其父母服十三日而除。当丧朝谒 两殿。则权着玉色服云云。 嫔宫持私亲之服。当其朝谒。不得不权着。事理诚然。而若夫 嫔宫之丧。于 大殿中殿。自是正统适子妇服。 两殿与 世子同服期年。本不可以私服例施之。则 进见时仍用白衣冠。自无嫌碍。礼亦当然。若变素为吉则或恐有损于事体。原任大臣所谓缟素嫌于通丧云者。亦似然矣。而但庚申 国恤时。 大殿纯用白衣冠之制。而不以通丧为嫌。则何独于今日。以此为拘耶。或曰。庚申年则 大殿当为杖期。今日 春宫则当为不杖期。杖与
不杖期章疏曰。此不杖期。轻于上禫杖。故次之。杖与不杖。虽曰不同。其正服齐衰裳皆同五升。而冠八升则不异也。据此不杖两期服色。元不有别。 大殿燕居服色。亦岂有异于 东宫燕居服色耶。然帝王家服制。多袭短丧之遗意。不用常礼者或有之。今此嫔宫丧。十三日未除衰带前。 大殿果能服素如礼。则便是改时制而从古礼之盛举。固无间然。而或与春宫差殊。用淡玉色衣制。恐不至为害否。至于 春宫视朝接下之时。元非压尊降屈之地。仍用燕居道服。以为视朝之制。似或无妨。又按后续录曰。 王世子嫔。为其父母服十三日而除。当丧朝谒 两殿。则权着玉色服云云。 嫔宫持私亲之服。当其朝谒。不得不权着。事理诚然。而若夫 嫔宫之丧。于 大殿中殿。自是正统适子妇服。 两殿与 世子同服期年。本不可以私服例施之。则 进见时仍用白衣冠。自无嫌碍。礼亦当然。若变素为吉则或恐有损于事体。原任大臣所谓缟素嫌于通丧云者。亦似然矣。而但庚申 国恤时。 大殿纯用白衣冠之制。而不以通丧为嫌。则何独于今日。以此为拘耶。或曰。庚申年则 大殿当为杖期。今日 春宫则当为不杖期。杖与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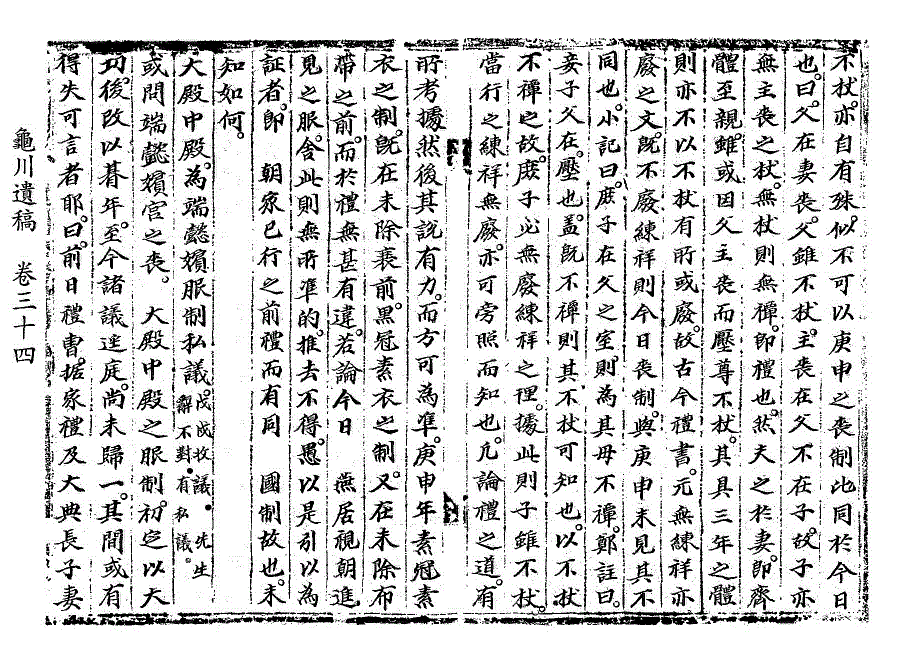 不杖。亦自有殊。似不可以庚申之丧制比同于今日也。曰。父在妻丧。父虽不杖。主丧在父不在子。故子亦无主丧之杖。无杖则无禫。即礼也。然夫之于妻。即齐体至亲。虽或因父主丧而压尊不杖。其具三年之体则亦不以不杖有所或废。故古今礼书。元无练祥亦废之文。既不废练祥则今日丧制。与庚申未见其不同也。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郑注曰。妾子父在。压也。盖既不禫则其不杖可知也。以不杖不禫之故。庶子必无废练祥之理。据此则子虽不杖。当行之练祥无废。亦可旁照而知也。凡论礼之道。有所考据然后其说有力。而方可为准。庚申年素冠素衣之制。既在未除衰前。黑冠素衣之制。又在未除布带之前。而于礼无甚有违。若论今日 燕居视朝进见之服。舍此则无所准的。推去不得。愚以是引以为证者。即 朝家已行之前礼而有同 国制故也。未知如何。
不杖。亦自有殊。似不可以庚申之丧制比同于今日也。曰。父在妻丧。父虽不杖。主丧在父不在子。故子亦无主丧之杖。无杖则无禫。即礼也。然夫之于妻。即齐体至亲。虽或因父主丧而压尊不杖。其具三年之体则亦不以不杖有所或废。故古今礼书。元无练祥亦废之文。既不废练祥则今日丧制。与庚申未见其不同也。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郑注曰。妾子父在。压也。盖既不禫则其不杖可知也。以不杖不禫之故。庶子必无废练祥之理。据此则子虽不杖。当行之练祥无废。亦可旁照而知也。凡论礼之道。有所考据然后其说有力。而方可为准。庚申年素冠素衣之制。既在未除衰前。黑冠素衣之制。又在未除布带之前。而于礼无甚有违。若论今日 燕居视朝进见之服。舍此则无所准的。推去不得。愚以是引以为证者。即 朝家已行之前礼而有同 国制故也。未知如何。大殿中殿。为端懿嫔服制私议。(戊戌收议。 先生辞不对。有私议。)
或问端懿嫔宫之丧。 大殿中殿之服制。初定以大功。后改以期年。至今诸议径庭。尚未归一。其间或有得失可言者耶。曰。前日礼曹。据家礼及大典长子妻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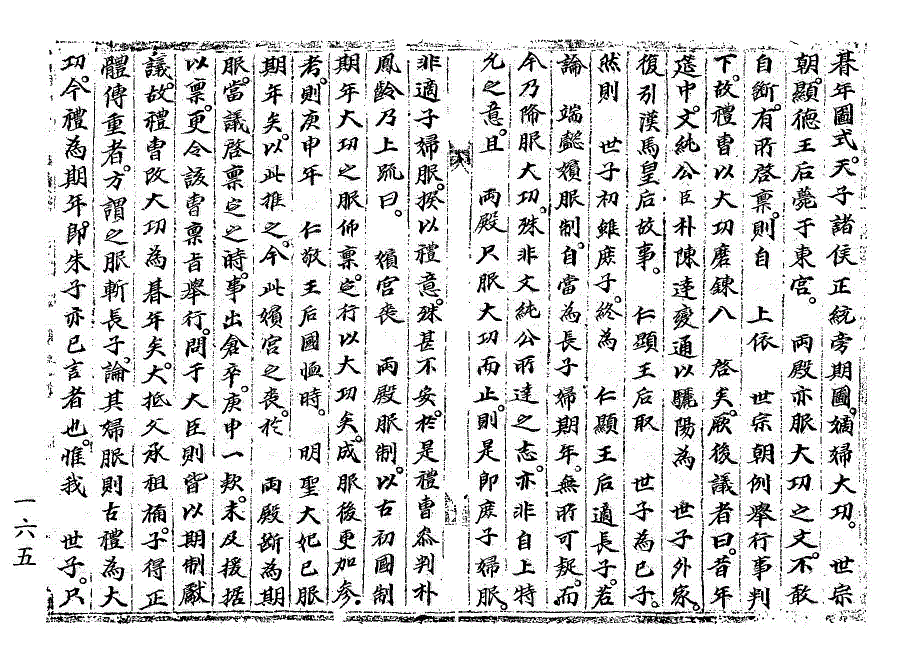 期年图式。天子诸侯正统旁期图。嫡妇大功。 世宗朝。显德王后薨于东宫。 两殿亦服大功之文。不敢自断。有所启禀。则自 上依 世宗朝例举行事判下。故礼曹以大功磨鍊入 启矣。厥后议者曰。昔年筵中。文纯公臣朴陈达变通以骊阳为 世子外家。复引汉马皇后故事。 仁显王后取 世子为己子。然则 世子初虽庶子。终为 仁显王后适长子。若论 端懿嫔服制。自当为长子妇期年。无所可疑。而今乃降服大功。殊非文纯公所达之志。亦非自上特允之意。且 两殿只服大功而止。则是即庶子妇服。非适子妇服。揆以礼意。殊甚不安。于是礼曹参判朴凤龄乃上疏曰。 嫔宫丧 两殿服制。以古初国制期年大功之服仰禀。定行以大功矣。成服后更加参考。则庚申年 仁敬王后国恤时。 明圣大妃已服期年矣。以此推之。今此嫔宫之丧。于 两殿断为期服。当议启禀定之时。事出仓卒。庚申一款。未及援据以禀。更令该曹禀旨举行。问于大臣则皆以期制献议。故礼曹改大功为期年矣。大抵父承祖祢。子得正体传重者。方谓之服斩长子。论其妇服则古礼为大功。今礼为期年。即朱子亦已言者也。惟我 世子。只
期年图式。天子诸侯正统旁期图。嫡妇大功。 世宗朝。显德王后薨于东宫。 两殿亦服大功之文。不敢自断。有所启禀。则自 上依 世宗朝例举行事判下。故礼曹以大功磨鍊入 启矣。厥后议者曰。昔年筵中。文纯公臣朴陈达变通以骊阳为 世子外家。复引汉马皇后故事。 仁显王后取 世子为己子。然则 世子初虽庶子。终为 仁显王后适长子。若论 端懿嫔服制。自当为长子妇期年。无所可疑。而今乃降服大功。殊非文纯公所达之志。亦非自上特允之意。且 两殿只服大功而止。则是即庶子妇服。非适子妇服。揆以礼意。殊甚不安。于是礼曹参判朴凤龄乃上疏曰。 嫔宫丧 两殿服制。以古初国制期年大功之服仰禀。定行以大功矣。成服后更加参考。则庚申年 仁敬王后国恤时。 明圣大妃已服期年矣。以此推之。今此嫔宫之丧。于 两殿断为期服。当议启禀定之时。事出仓卒。庚申一款。未及援据以禀。更令该曹禀旨举行。问于大臣则皆以期制献议。故礼曹改大功为期年矣。大抵父承祖祢。子得正体传重者。方谓之服斩长子。论其妇服则古礼为大功。今礼为期年。即朱子亦已言者也。惟我 世子。只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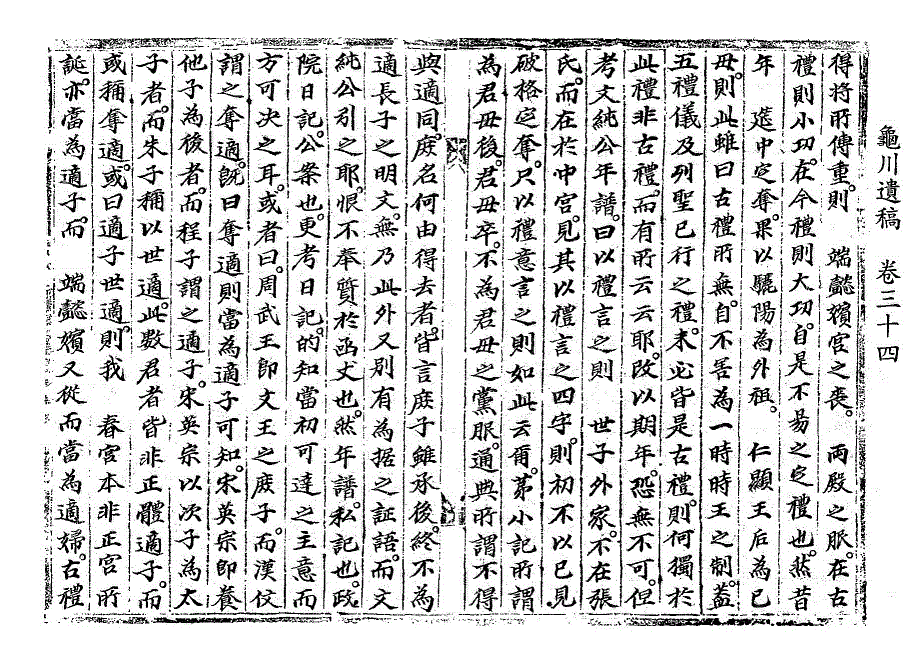 得将所传重。则 端懿嫔宫之丧。 两殿之服。在古礼则小功。在今礼则大功。自是不易之定礼也。然昔年 筵中定夺。果以骊阳为外祖。 仁显王后为己母。则此虽曰古礼所无。自不害为一时时王之制。盖五礼仪及列圣已行之礼。未必皆是古礼。则何独于此礼非古礼。而有所云云耶。改以期年。恐无不可。但考文纯公年谱。曰以礼言之则 世子外家。不在张氏。而在于中宫。见其以礼言之四字。则初不以己见破格定夺。只以礼意言之则如此云尔。第小记所谓为君母后。君母卒。不为君母之党服。通典所谓不得与适同。庶名何由得去者。皆言庶子虽承后。终不为适长子之明文。无乃此外又别有为据之证语。而文纯公引之耶。恨不奉质于函丈也。然年谱。私记也。政院日记。公案也。更考日记。的知当初可达之主意而方可决之耳。或者曰。周武王即文王之庶子。而汉伩谓之夺适。既曰夺适则当为适子可知。宋英宗即养他子为后者。而程子谓之适子。宋英宗以次子为太子者。而朱子称以世适。此数君者皆非正体适子。而或称夺适。或曰适子世适。则我 春宫本非正宫所诞。亦当为适子。而 端懿嫔又从而当为适妇。古礼
得将所传重。则 端懿嫔宫之丧。 两殿之服。在古礼则小功。在今礼则大功。自是不易之定礼也。然昔年 筵中定夺。果以骊阳为外祖。 仁显王后为己母。则此虽曰古礼所无。自不害为一时时王之制。盖五礼仪及列圣已行之礼。未必皆是古礼。则何独于此礼非古礼。而有所云云耶。改以期年。恐无不可。但考文纯公年谱。曰以礼言之则 世子外家。不在张氏。而在于中宫。见其以礼言之四字。则初不以己见破格定夺。只以礼意言之则如此云尔。第小记所谓为君母后。君母卒。不为君母之党服。通典所谓不得与适同。庶名何由得去者。皆言庶子虽承后。终不为适长子之明文。无乃此外又别有为据之证语。而文纯公引之耶。恨不奉质于函丈也。然年谱。私记也。政院日记。公案也。更考日记。的知当初可达之主意而方可决之耳。或者曰。周武王即文王之庶子。而汉伩谓之夺适。既曰夺适则当为适子可知。宋英宗即养他子为后者。而程子谓之适子。宋英宗以次子为太子者。而朱子称以世适。此数君者皆非正体适子。而或称夺适。或曰适子世适。则我 春宫本非正宫所诞。亦当为适子。而 端懿嫔又从而当为适妇。古礼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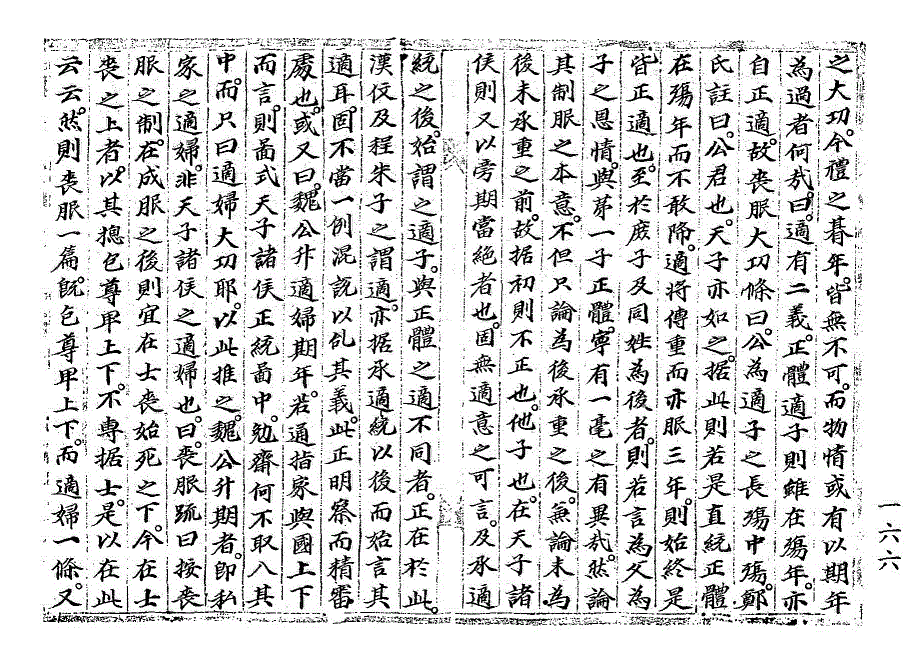 之大功。今礼之期年。皆无不可。而物情或有以期年为过者何哉。曰。适有二义。正体适子则虽在殇年。亦自正适。故丧服大功条曰。公为适子之长殇中殇。郑氏注曰。公君也。天子亦如之。据此则若是直统正体在殇年而不敢降。适将传重而亦服三年。则始终是皆正适也。至于庶子及同姓为后者。则若言为父为子之恩情。与第一子正体。宁有一毫之有异哉。然论其制服之本意。不但只论为后承重之后。兼论未为后未承重之前。故据初则不正也。他子也。在天子诸侯则又以旁期当绝者也。固无适意之可言。及承适统之后。始谓之适子。与正体之适不同者。正在于此。汉伩及程朱子之谓适。亦据承适统以后而始言其适耳。固不当一例混说以乱其义。此正明察而精审处也。或又曰。魏公升适妇期年。若通指家与国上下而言。则啚式天子诸侯正统啚中。勉斋何不取入其中。而只曰适妇大功耶。以此推之。魏公升期者。即私家之适妇。非天子诸侯之适妇也。曰。丧服疏曰按丧服之制。在成服之后则宜在士丧始死之下。今在士丧之上者。以其总包尊卑上下。不专据士。是以在此云云。然则丧服一篇。既包尊卑上下。而适妇一条。又
之大功。今礼之期年。皆无不可。而物情或有以期年为过者何哉。曰。适有二义。正体适子则虽在殇年。亦自正适。故丧服大功条曰。公为适子之长殇中殇。郑氏注曰。公君也。天子亦如之。据此则若是直统正体在殇年而不敢降。适将传重而亦服三年。则始终是皆正适也。至于庶子及同姓为后者。则若言为父为子之恩情。与第一子正体。宁有一毫之有异哉。然论其制服之本意。不但只论为后承重之后。兼论未为后未承重之前。故据初则不正也。他子也。在天子诸侯则又以旁期当绝者也。固无适意之可言。及承适统之后。始谓之适子。与正体之适不同者。正在于此。汉伩及程朱子之谓适。亦据承适统以后而始言其适耳。固不当一例混说以乱其义。此正明察而精审处也。或又曰。魏公升适妇期年。若通指家与国上下而言。则啚式天子诸侯正统啚中。勉斋何不取入其中。而只曰适妇大功耶。以此推之。魏公升期者。即私家之适妇。非天子诸侯之适妇也。曰。丧服疏曰按丧服之制。在成服之后则宜在士丧始死之下。今在士丧之上者。以其总包尊卑上下。不专据士。是以在此云云。然则丧服一篇。既包尊卑上下。而适妇一条。又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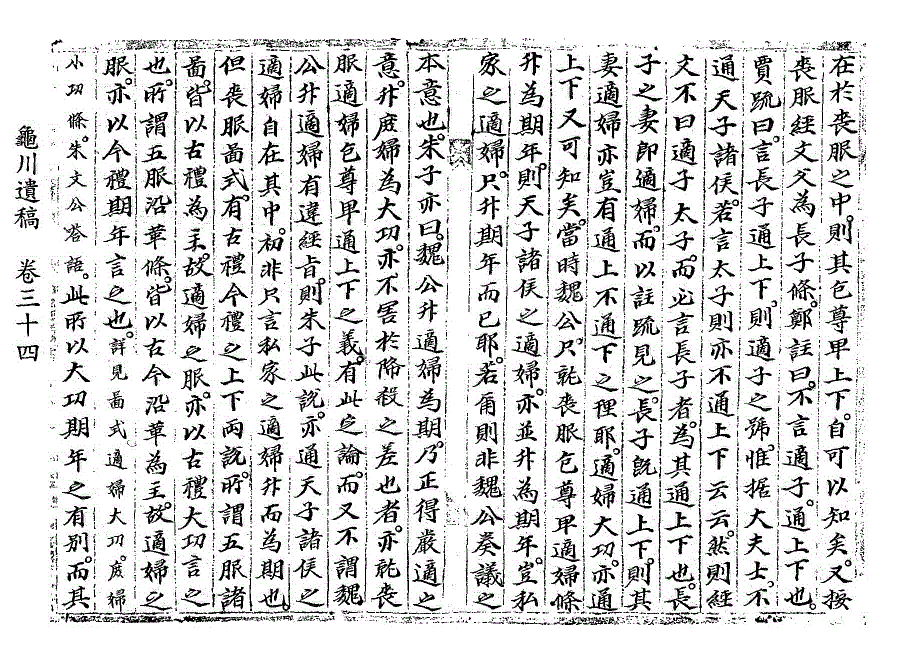 在于丧服之中。则其包尊卑上下。自可以知矣。又按丧服经文父为长子条。郑注曰。不言适子。通上下也。贾疏曰。言长子通上下。则适子之号。惟据大夫士。不通天子诸侯。若言太子则亦不通上下云云。然则经文不曰适子太子。而必言长子者。为其通上下也。长子之妻即适妇。而以注疏见之。长子既通上下。则其妻适妇亦岂有通上不通下之理耶。适妇大功。亦通上下又可知矣。当时魏公。只就丧服包尊卑适妇条升为期年。则天子诸侯之适妇。亦并升为期年。岂私家之适妇。只升期年而已耶。若尔则非魏公奏议之本意也。朱子亦曰。魏公升适妇为期。乃正得严适之意。升庶妇为大功。亦不害于降杀之差也者。亦就丧服适妇包尊卑通上下之义。有此定论。而又不谓魏公升适妇有违经旨。则朱子此说。亦通天子诸侯之适妇自在其中。初非只言私家之适妇升而为期也。但丧服啚式。有古礼今礼之上下两说。所谓五服诸啚。皆以古礼为主。故适妇之服。亦以古礼大功言之也。所谓五服沿革条。皆以古今沿革为主。故适妇之服。亦以今礼期年言之也。(详见啚式。适妇大功。庶妇小功条。朱文公答语。)此所以大功期年之有别。而其
在于丧服之中。则其包尊卑上下。自可以知矣。又按丧服经文父为长子条。郑注曰。不言适子。通上下也。贾疏曰。言长子通上下。则适子之号。惟据大夫士。不通天子诸侯。若言太子则亦不通上下云云。然则经文不曰适子太子。而必言长子者。为其通上下也。长子之妻即适妇。而以注疏见之。长子既通上下。则其妻适妇亦岂有通上不通下之理耶。适妇大功。亦通上下又可知矣。当时魏公。只就丧服包尊卑适妇条升为期年。则天子诸侯之适妇。亦并升为期年。岂私家之适妇。只升期年而已耶。若尔则非魏公奏议之本意也。朱子亦曰。魏公升适妇为期。乃正得严适之意。升庶妇为大功。亦不害于降杀之差也者。亦就丧服适妇包尊卑通上下之义。有此定论。而又不谓魏公升适妇有违经旨。则朱子此说。亦通天子诸侯之适妇自在其中。初非只言私家之适妇升而为期也。但丧服啚式。有古礼今礼之上下两说。所谓五服诸啚。皆以古礼为主。故适妇之服。亦以古礼大功言之也。所谓五服沿革条。皆以古今沿革为主。故适妇之服。亦以今礼期年言之也。(详见啚式。适妇大功。庶妇小功条。朱文公答语。)此所以大功期年之有别。而其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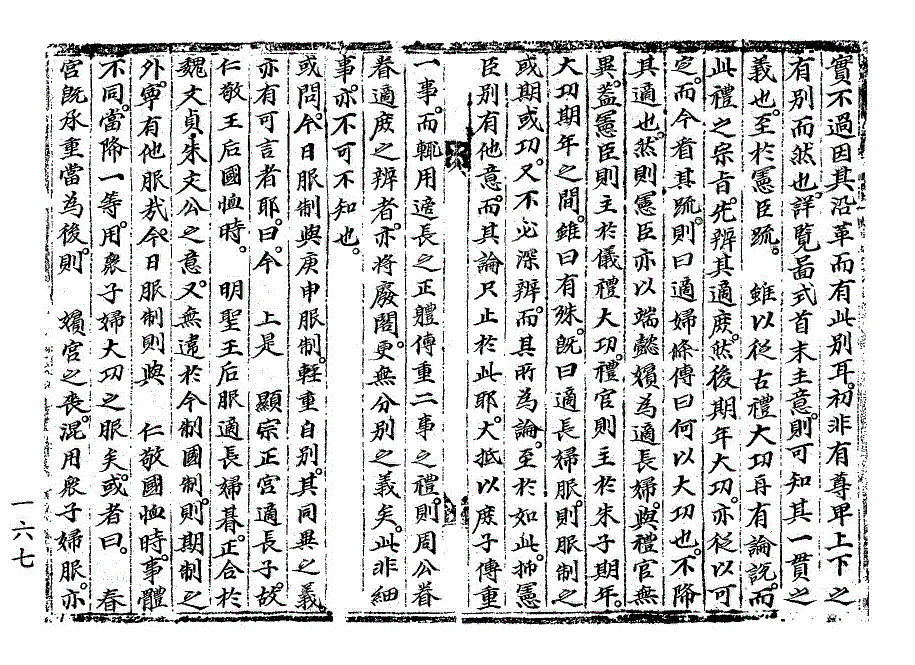 实不过因其沿革而有此别耳。初非有尊卑上下之有别而然也。详览啚式首末主意。则可知其一贯之义也。至于宪臣疏。 虽以从古礼大功再有论说。而此礼之宗旨。先辨其适庶。然后期年大功。亦从以可定。而今看其疏。则曰适妇条传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适也。然则宪臣亦以端懿嫔为适长妇。与礼官无异。盖宪臣则主于仪礼大功。礼官则主于朱子期年。大功期年之间。虽曰有殊。既曰适长妇服。则服制之或期或功。又不必深辨。而其所为论。至于如此。抑宪臣别有他意。而其论只止于此耶。大抵以庶子传重一事。而辄用适长之正体传重二事之礼。则周公眷眷适庶之辨者。亦将废阁。更无分别之义矣。此非细事。亦不可不知也。
实不过因其沿革而有此别耳。初非有尊卑上下之有别而然也。详览啚式首末主意。则可知其一贯之义也。至于宪臣疏。 虽以从古礼大功再有论说。而此礼之宗旨。先辨其适庶。然后期年大功。亦从以可定。而今看其疏。则曰适妇条传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适也。然则宪臣亦以端懿嫔为适长妇。与礼官无异。盖宪臣则主于仪礼大功。礼官则主于朱子期年。大功期年之间。虽曰有殊。既曰适长妇服。则服制之或期或功。又不必深辨。而其所为论。至于如此。抑宪臣别有他意。而其论只止于此耶。大抵以庶子传重一事。而辄用适长之正体传重二事之礼。则周公眷眷适庶之辨者。亦将废阁。更无分别之义矣。此非细事。亦不可不知也。或问。今日服制与庚申服制。轻重自别。其同异之义。亦有可言者耶。曰。今 上是 显宗正宫适长子。故仁敬王后国恤时。 明圣王后服适长妇期。正合于魏文贞,朱文公之意。又无违于今制国制。则期制之外。宁有他服哉。今日服制则与 仁敬国恤时。事体不同。当降一等。用众子妇大功之服矣。或者曰。 春宫既承重当为后。则 嫔宫之丧。混用众子妇服。亦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8H 页
 不未安乎。曰。大功章云。为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服。据此而见之。国君绝期已下。而以其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而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也。今 春宫既升嫡而与尊者为一体矣。将承重而继 宗庙之大统矣。此即与 大殿尊同。而 嫔宫又与 春宫齐体。则其尊同于 大殿。又奚异于 春宫耶。是以自 上服嫔宫大功。亦出于尊同之尊。此岂他 王子夫人绝而无服者。所可比拟耶。亦何可以混用为虑耶。又按丧服适妇条。小记郑注曰。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妇。将所传重者非适。服之皆如庶子庶妇也。孔疏曰。将所传重非适者。为无适子。以庶子传重及养他子为后者也。然则今 大殿服嫔宫庶妇之服。实遵郑注之意。不可遽以为非也。盖礼得正体传重二事者。父母为长子三年。舅姑为适妇期年也。至于长子之弟及妾子。则虽曰将所传重。其于二事。只得其一而不得其一。故不为长子与适妇之服。而服其本服。郑注所言。亦本于此也。
不未安乎。曰。大功章云。为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服。据此而见之。国君绝期已下。而以其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而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也。今 春宫既升嫡而与尊者为一体矣。将承重而继 宗庙之大统矣。此即与 大殿尊同。而 嫔宫又与 春宫齐体。则其尊同于 大殿。又奚异于 春宫耶。是以自 上服嫔宫大功。亦出于尊同之尊。此岂他 王子夫人绝而无服者。所可比拟耶。亦何可以混用为虑耶。又按丧服适妇条。小记郑注曰。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妇。将所传重者非适。服之皆如庶子庶妇也。孔疏曰。将所传重非适者。为无适子。以庶子传重及养他子为后者也。然则今 大殿服嫔宫庶妇之服。实遵郑注之意。不可遽以为非也。盖礼得正体传重二事者。父母为长子三年。舅姑为适妇期年也。至于长子之弟及妾子。则虽曰将所传重。其于二事。只得其一而不得其一。故不为长子与适妇之服。而服其本服。郑注所言。亦本于此也。与金直卿
来说曰。按通典庾蔚之曰。丧服传长子三年。言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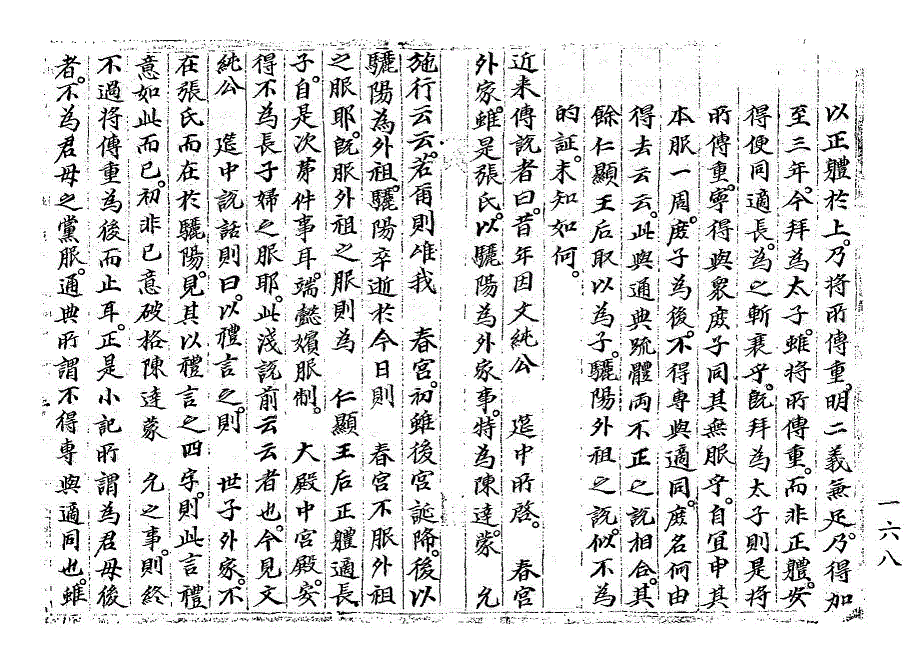 以正体于上。乃将所传重。明二义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为太子。虽将所传重。而非正体。安得便同适长。为之斩衰乎。既拜为太子则是将所传重。宁得与众庶子同其无服乎。自宜申其本服一周。庶子为后。不得专与适同。庶名何由得去云云。此与通典疏体两不正之说相合。其馀仁显王后取以为子。骊阳外祖之说。似不为的证。未知如何。
以正体于上。乃将所传重。明二义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为太子。虽将所传重。而非正体。安得便同适长。为之斩衰乎。既拜为太子则是将所传重。宁得与众庶子同其无服乎。自宜申其本服一周。庶子为后。不得专与适同。庶名何由得去云云。此与通典疏体两不正之说相合。其馀仁显王后取以为子。骊阳外祖之说。似不为的证。未知如何。近来传说者曰。昔年因文纯公 筵中所启。 春宫外家。虽是张氏。以骊阳为外家事。特为陈达。蒙 允施行云云。若尔则唯我 春宫。初虽后宫诞降。后以骊阳为外祖。骊阳卒逝于今日则 春宫不服外祖之服耶。既服外祖之服则为 仁显王后正体适长子。自是次第件事耳。端懿嫔服制。 大殿中宫殿。安得不为长子妇之服耶。此浅说前云云者也。今见文纯公 筵中说话则曰。以礼言之。则 世子外家。不在张氏而在于骊阳。见其以礼言之四字。则此言礼意如此而已。初非己意破格陈达蒙 允之事。则终不过将传重为后而止耳。正是小记所谓为君母后者。不为君母之党服。通典所谓不得专与适同也。虽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9H 页
 据礼而言。骊阳不为 春宫外家。亦似明白。来说所云。恐皆得之。
据礼而言。骊阳不为 春宫外家。亦似明白。来说所云。恐皆得之。答李仲晖
端懿嫔服制私议。谨已闻命而犹有所疑。今 春宫虽以骊阳为外祖。终非天属也。凡帝王家众庶子或旁支入承者。皆以承统帝王为父。则承统帝王之后自当为母。承统帝王之后为母。则母之父自当为外祖。执此而指众庶子旁支而皆为正后之出耶。然则四种中体而不正之说无用处。盖取为子之礼。终有间于天属之亲而然也。故鄙意以盛说上款语为准。未知如何。更仰回教。
此段所论。终异于浅见矣。凡帝王家后宫所生承统者。虽以其帝王为父。帝王妃为正母。其外祖父母则以其本生母之父母而无变也。何以知其然也。续解丧服为外祖父母条。本经记曰。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无服。丧服小记曰。为君母后者。君母卒则不为君母之党服。郑注曰。徒从也。所从亡则已。疏曰。为君母后者。谓无适立庶为后也。妾子之于君母之党。悉徒从。若君母卒则不服君母之党。惟我 春宫承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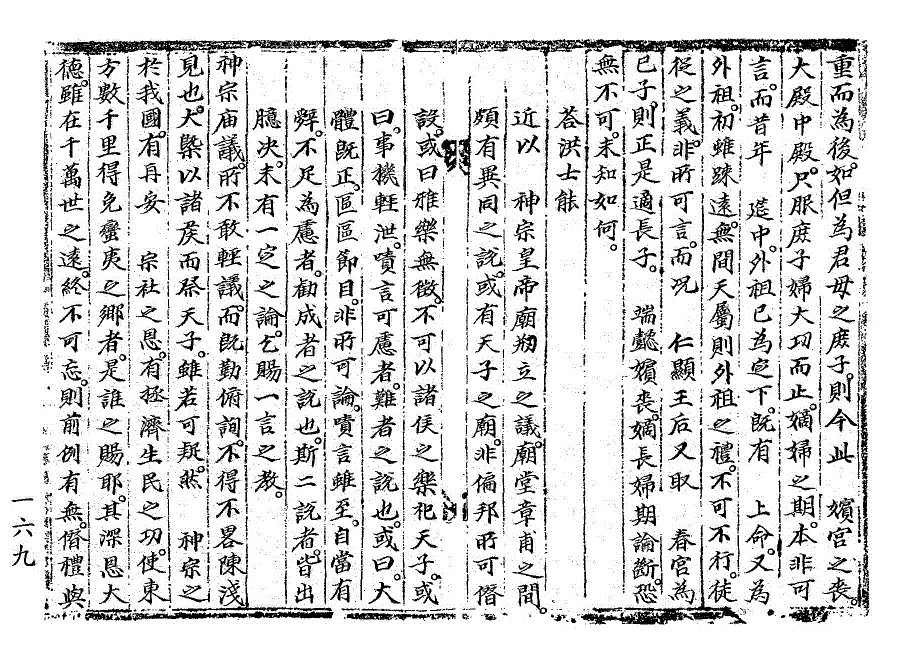 重而为后。如但为君母之庶子。则今此 嫔宫之丧。大殿中殿。只服庶子妇大功而止。嫡妇之期。本非可言。而昔年 筵中。外祖已为定下。既有 上命。又为外祖。初虽疏远。无间天属则外祖之礼。不可不行。徒从之义。非所可言。而况 仁显王后又取 春宫为己子。则正是适长子。 端懿嫔丧。嫡长妇期论断。恐无不可。未知如何。
重而为后。如但为君母之庶子。则今此 嫔宫之丧。大殿中殿。只服庶子妇大功而止。嫡妇之期。本非可言。而昔年 筵中。外祖已为定下。既有 上命。又为外祖。初虽疏远。无间天属则外祖之礼。不可不行。徒从之义。非所可言。而况 仁显王后又取 春宫为己子。则正是适长子。 端懿嫔丧。嫡长妇期论断。恐无不可。未知如何。答洪士能
近以 神宗皇帝庙刱立之议。庙堂章甫之间。颇有异同之说。或有天子之庙。非偏邦所可僭设。或曰雅乐无徵。不可以诸侯之乐祀天子。或曰。事机轻泄。啧言可虑者。难者之说也。或曰。大体既正。区区节目。非所可论。啧言虽至。自当有辞。不足为虑者。劝成者之说也。斯二说者。皆出臆决。未有一定之论。乞赐一言之教。
神宗庙议。所不敢轻议。而既勤俯询。不得不略陈浅见也。大槩以诸侯而祭天子。虽若可疑。然 神宗之于我国。有再安 宗社之恩。有拯济生民之功。使东方数千里得免蛮夷之乡者。是谁之赐耶。其深恩大德。虽在千万世之远。终不可忘。则前例有无。僭礼与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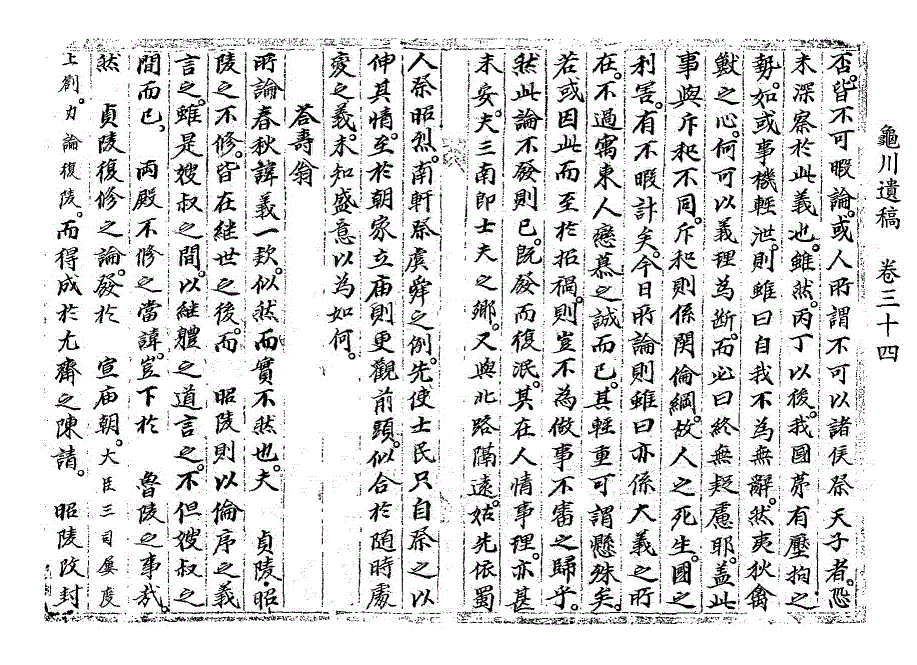 否。皆不可暇论。或人所谓不可以诸侯祭天子者。恐未深察于此义也。虽然。丙丁以后。我国第有压拘之势。如或事机轻泄。则虽曰自我不为无辞。然夷狄禽兽之心。何可以义理为断。而必曰终无疑虑耶。盖此事与斥和不同。斥和则系关伦纲。故人之死生。国之利害。有不暇计矣。今日所论则虽曰亦系大义之所在。不过寓东人恋慕之诚而已。其轻重可谓悬殊矣。若或因此而至于招祸。则岂不为做事不审之归乎。然此论不发则已。既发而复泯。其在人情事理。亦甚未安。夫三南即士夫之乡。又与北路隔远。姑先依蜀人祭昭烈。南轩祭虞舜之例。先使士民只自祭之以伸其情。至于朝家立庙则更观前头。似合于随时处变之义。未知盛意以为如何。
否。皆不可暇论。或人所谓不可以诸侯祭天子者。恐未深察于此义也。虽然。丙丁以后。我国第有压拘之势。如或事机轻泄。则虽曰自我不为无辞。然夷狄禽兽之心。何可以义理为断。而必曰终无疑虑耶。盖此事与斥和不同。斥和则系关伦纲。故人之死生。国之利害。有不暇计矣。今日所论则虽曰亦系大义之所在。不过寓东人恋慕之诚而已。其轻重可谓悬殊矣。若或因此而至于招祸。则岂不为做事不审之归乎。然此论不发则已。既发而复泯。其在人情事理。亦甚未安。夫三南即士夫之乡。又与北路隔远。姑先依蜀人祭昭烈。南轩祭虞舜之例。先使士民只自祭之以伸其情。至于朝家立庙则更观前头。似合于随时处变之义。未知盛意以为如何。答寿翁
所论春秋讳义一款。似然而实不然也。夫 贞陵,昭陵之不修。皆在继世之后。而 昭陵则以伦序之义言之。虽是嫂叔之间。以继体之道言之。不但嫂叔之间而已。 两殿不修之当讳。岂下于 鲁陵之事哉。然 贞陵复修之论。发于 宣庙朝。(大臣三司屡度上劄。力论复陵。)而得成于尤斋之陈请。 昭陵改封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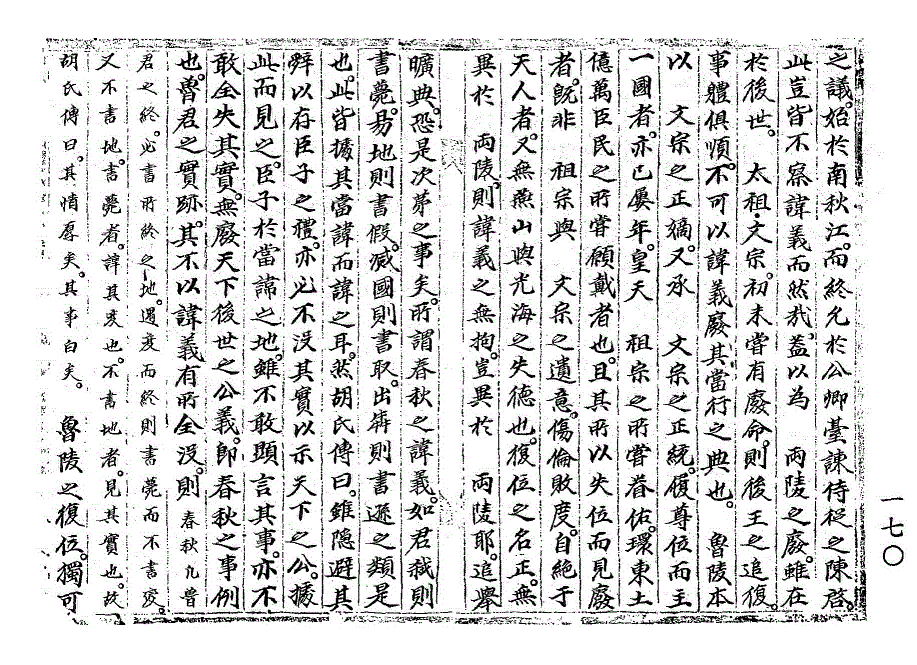 之议。始于南秋江。而终允于公卿台谏侍从之陈启。此岂皆不察讳义而然哉。盖以为 两陵之废。虽在于后世。 太祖,文宗。初未尝有废命。则后王之追复。事体俱顺。不可以讳义废其当行之典也。 鲁陵本以 文宗之正嫡。又承 文宗之正统。履尊位而主一国者。亦已屡年。皇天 祖宗之所尝眷佑。环东土亿万臣民之所尝愿戴者也。且其所以失位而见废者。既非 祖宗与 文宗之遗意。伤伦败度。自绝于天人者。又无燕山与光海之失德也。复位之名正。无异于 两陵。则讳义之无拘。岂异于 两陵耶。追举旷典。恐是次第之事矣。所谓春秋之讳义。如君弑则书薨。易地则书假。灭国则书取。出奔则书逊之类是也。此皆据其当讳而讳之耳。然胡氏传曰。虽隐避其辞以存臣子之礼。亦必不没其实以示天下之公。据此而见之。臣子于当讳之地。虽不敢显言其事。亦不敢全失其实。无废天下后世之公义。即春秋之事例也。鲁君之实迹。其不以讳义有所全没。则(春秋凡鲁君之终。必书所终之地。遇变而终则书薨而不书变。又不书地。书薨者。讳其变也。不书地者。见其实也。故胡氏传曰。其情厚矣。其事白矣。) 鲁陵之复位。独可
之议。始于南秋江。而终允于公卿台谏侍从之陈启。此岂皆不察讳义而然哉。盖以为 两陵之废。虽在于后世。 太祖,文宗。初未尝有废命。则后王之追复。事体俱顺。不可以讳义废其当行之典也。 鲁陵本以 文宗之正嫡。又承 文宗之正统。履尊位而主一国者。亦已屡年。皇天 祖宗之所尝眷佑。环东土亿万臣民之所尝愿戴者也。且其所以失位而见废者。既非 祖宗与 文宗之遗意。伤伦败度。自绝于天人者。又无燕山与光海之失德也。复位之名正。无异于 两陵。则讳义之无拘。岂异于 两陵耶。追举旷典。恐是次第之事矣。所谓春秋之讳义。如君弑则书薨。易地则书假。灭国则书取。出奔则书逊之类是也。此皆据其当讳而讳之耳。然胡氏传曰。虽隐避其辞以存臣子之礼。亦必不没其实以示天下之公。据此而见之。臣子于当讳之地。虽不敢显言其事。亦不敢全失其实。无废天下后世之公义。即春秋之事例也。鲁君之实迹。其不以讳义有所全没。则(春秋凡鲁君之终。必书所终之地。遇变而终则书薨而不书变。又不书地。书薨者。讳其变也。不书地者。见其实也。故胡氏传曰。其情厚矣。其事白矣。) 鲁陵之复位。独可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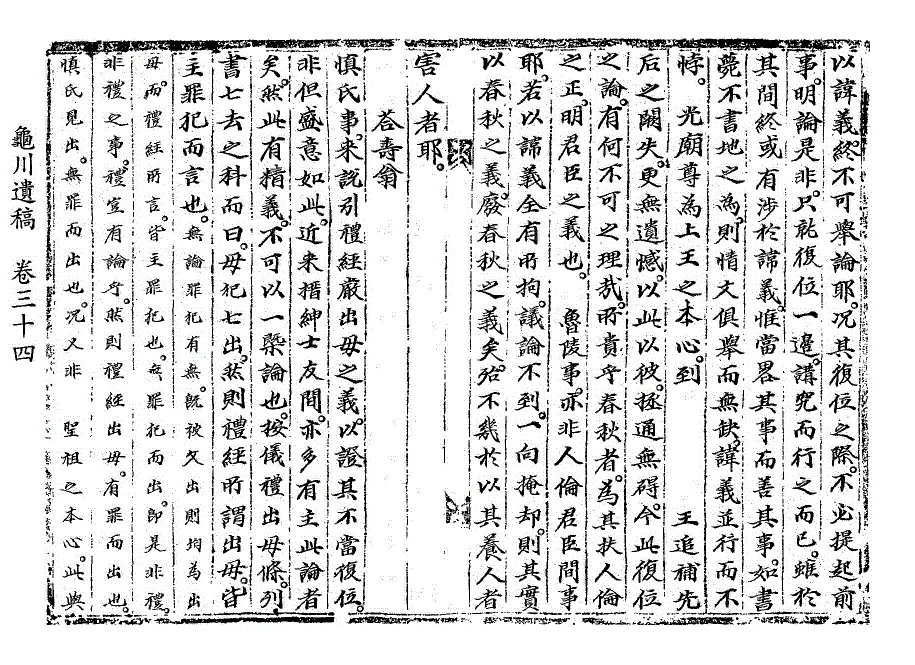 以讳义。终不可举论耶。况其复位之际。不必提起前事。明论是非。只就复位一边。讲究而行之而已。虽于其间终或有涉于讳义。惟当略其事而善其事。如书薨不书地之为。则情文俱举而无缺。讳义并行而不悖。 光庙尊为上王之本心。到▣▣▣▣王追补先后之阙失。更无遗憾。以此以彼。拯通无碍。今此复位之论。有何不可之理哉。所贵乎春秋者。为其扶人伦之正。明君臣之义也。 鲁陵事。亦非人伦君臣间事耶。若以讳义全有所拘。议论不到。一向掩却。则其实以春秋之义。废春秋之义矣。殆不几于以其养人者害人者耶。
以讳义。终不可举论耶。况其复位之际。不必提起前事。明论是非。只就复位一边。讲究而行之而已。虽于其间终或有涉于讳义。惟当略其事而善其事。如书薨不书地之为。则情文俱举而无缺。讳义并行而不悖。 光庙尊为上王之本心。到▣▣▣▣王追补先后之阙失。更无遗憾。以此以彼。拯通无碍。今此复位之论。有何不可之理哉。所贵乎春秋者。为其扶人伦之正。明君臣之义也。 鲁陵事。亦非人伦君臣间事耶。若以讳义全有所拘。议论不到。一向掩却。则其实以春秋之义。废春秋之义矣。殆不几于以其养人者害人者耶。答寿翁
慎氏事。来说引礼经严出母之义。以證其不当复位。非但盛意如此。近来搢绅士友间。亦多有主此论者矣。然此有精义。不可以一槩论也。按仪礼出母条。列书七去之科而曰。母犯七出。然则礼经所谓出母。皆主罪犯而言也。(无论罪犯有无。既被父出则均为出母。而礼经所言。皆主罪犯也。无罪犯而出。即是非礼。非礼之事。礼岂有论乎。然则礼经出母。有罪而出也。慎氏见出。无罪而出也。况又非 圣祖之本心。此与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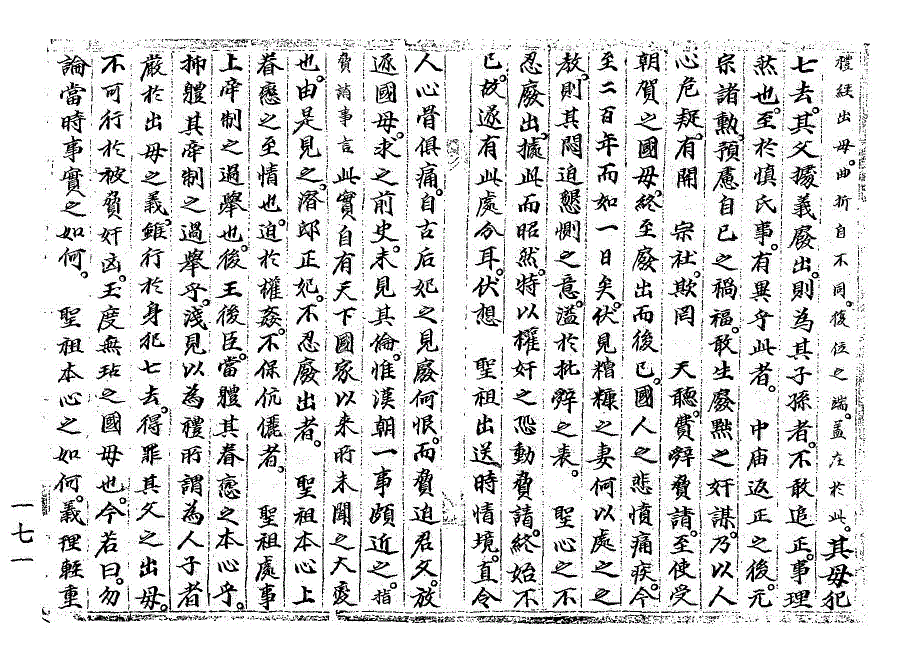 礼经出母。曲折自不同。复位之端。盖在于此。)其母犯七去。其父据义废出。则为其子孙者。不敢追正。事理然也。至于慎氏事。有异乎此者。 中庙返正之后。元宗诸勋。预虑自己之祸福。敢生废黜之奸谋。乃以人心危疑。有开 宗社。欺罔 天听。费辞䝱请。至使受朝贺之国母。终至废出而后已。国人之悲愤痛疾。今至二百年而如一日矣。伏见糟糠之妻何以处之之教。则其闷迫恳恻之意。溢于批辞之表。 圣心之不忍废出。据此而昭然。特以权奸之恐动䝱请。终始不已。故遂有此处分耳。伏想 圣祖出送时情境。直令人心骨俱痛。自古后妃之见废何恨。而䝱迫君父。放逐国母。求之前史。未见其伦。惟汉朝一事颇近之。(指䝱请事言)此实自有天下国家以来所未闻之大变也。由是见之。潜邸正妃。不忍废出者。 圣祖本心上眷恋之至情也。迫于权奸。不保伉俪者。 圣祖处事上牵制之过举也。后王后臣。当体其眷恋之本心乎。抑体其牵制之过举乎。浅见以为礼所谓为人子者严于出母之义。虽行于身犯七去。得罪其父之出母。不可行于被䝱奸凶。玉度无玷之国母也。今若曰。勿论当时事实之如何。 圣祖本心之如何。义理轻重
礼经出母。曲折自不同。复位之端。盖在于此。)其母犯七去。其父据义废出。则为其子孙者。不敢追正。事理然也。至于慎氏事。有异乎此者。 中庙返正之后。元宗诸勋。预虑自己之祸福。敢生废黜之奸谋。乃以人心危疑。有开 宗社。欺罔 天听。费辞䝱请。至使受朝贺之国母。终至废出而后已。国人之悲愤痛疾。今至二百年而如一日矣。伏见糟糠之妻何以处之之教。则其闷迫恳恻之意。溢于批辞之表。 圣心之不忍废出。据此而昭然。特以权奸之恐动䝱请。终始不已。故遂有此处分耳。伏想 圣祖出送时情境。直令人心骨俱痛。自古后妃之见废何恨。而䝱迫君父。放逐国母。求之前史。未见其伦。惟汉朝一事颇近之。(指䝱请事言)此实自有天下国家以来所未闻之大变也。由是见之。潜邸正妃。不忍废出者。 圣祖本心上眷恋之至情也。迫于权奸。不保伉俪者。 圣祖处事上牵制之过举也。后王后臣。当体其眷恋之本心乎。抑体其牵制之过举乎。浅见以为礼所谓为人子者严于出母之义。虽行于身犯七去。得罪其父之出母。不可行于被䝱奸凶。玉度无玷之国母也。今若曰。勿论当时事实之如何。 圣祖本心之如何。义理轻重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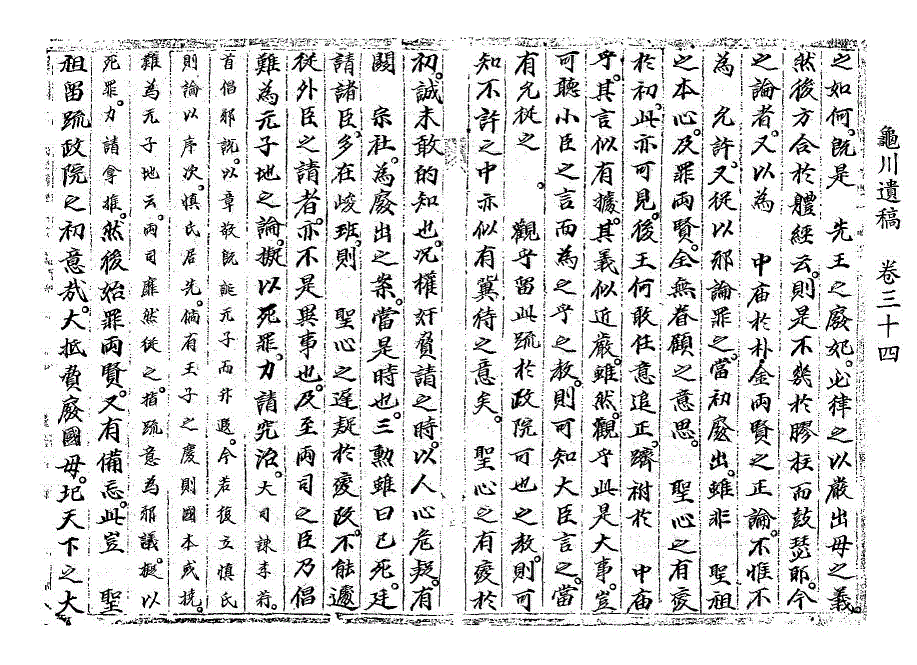 之如何。既是 先王之废妃。必律之以严出母之义。然后方合于体(一作礼)经云。则是不几于胶柱而鼓瑟耶。今之论者。又以为 中庙于朴,金两贤之正论。不惟不为 允许。又从以邪论罪之。当初废出。虽非 圣祖之本心。及罪两贤。全无眷顾之意思。 圣心之有变于初。此亦可见。后王何敢任意追正。跻祔于 中庙乎。其言似有据。其义似近严。虽然。观乎此是大事。岂可听小臣之言而为之乎之教。则可知大臣言之。当有允从之▣。▣观乎留此疏于政院可也之教。则可知不许之中亦似有冀待之意矣。 圣心之有变于初。诚未敢的知也。况权奸䝱请之时。以人心危疑。有关 宗社。为废出之案。当是时也。三勋虽曰已死。廷请诸臣。多在峻班。则 圣心之迟疑于变改。不能遽从外臣之请者。亦不是异事也。及至两司之臣乃倡难为元子地之论。拟以死罪。力请究治。(大司谏李荇。首倡邪说。以章敬既诞元子而升遐。今若复立慎氏则论以序次。慎氏居先。倘有王子之庆则国本或挠。难为元子地云。两司靡然从之。指疏意为邪议。拟以死罪。力请拿推。)然后始罪两贤。又有备忘。此岂 圣祖留疏政院之初意哉。大抵䝱废国母。圮天下之大
之如何。既是 先王之废妃。必律之以严出母之义。然后方合于体(一作礼)经云。则是不几于胶柱而鼓瑟耶。今之论者。又以为 中庙于朴,金两贤之正论。不惟不为 允许。又从以邪论罪之。当初废出。虽非 圣祖之本心。及罪两贤。全无眷顾之意思。 圣心之有变于初。此亦可见。后王何敢任意追正。跻祔于 中庙乎。其言似有据。其义似近严。虽然。观乎此是大事。岂可听小臣之言而为之乎之教。则可知大臣言之。当有允从之▣。▣观乎留此疏于政院可也之教。则可知不许之中亦似有冀待之意矣。 圣心之有变于初。诚未敢的知也。况权奸䝱请之时。以人心危疑。有关 宗社。为废出之案。当是时也。三勋虽曰已死。廷请诸臣。多在峻班。则 圣心之迟疑于变改。不能遽从外臣之请者。亦不是异事也。及至两司之臣乃倡难为元子地之论。拟以死罪。力请究治。(大司谏李荇。首倡邪说。以章敬既诞元子而升遐。今若复立慎氏则论以序次。慎氏居先。倘有王子之庆则国本或挠。难为元子地云。两司靡然从之。指疏意为邪议。拟以死罪。力请拿推。)然后始罪两贤。又有备忘。此岂 圣祖留疏政院之初意哉。大抵䝱废国母。圮天下之大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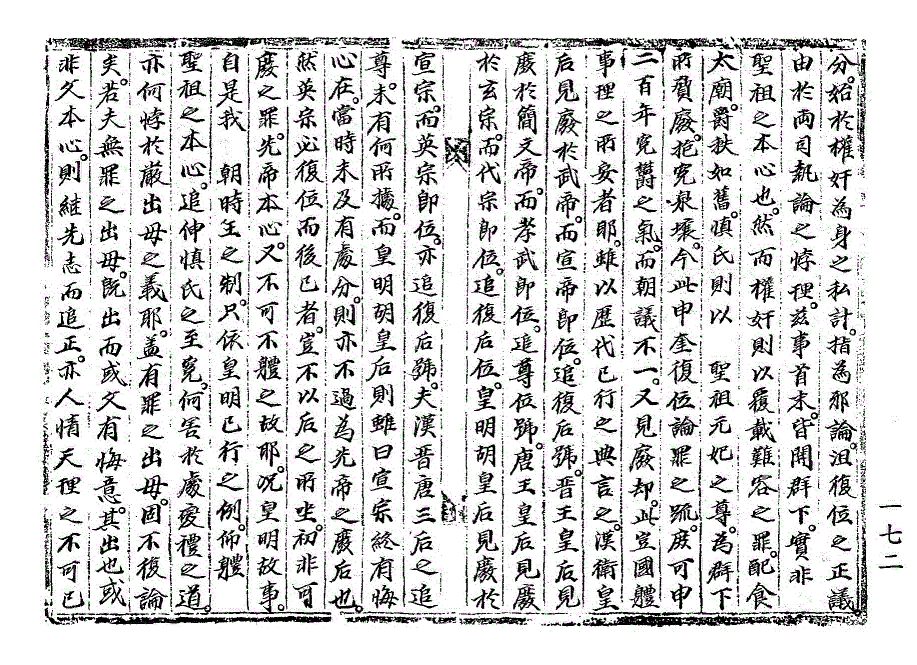 分。始于权奸为身之私计。指为邪论。沮复位之正议。由于两司执论之悖理。玆事首末。皆开群下。实非 圣祖之本心也。然而权奸则以覆载难容之罪。配食太庙。爵秩如旧。慎氏则以 圣祖元妃之尊。为群下所䝱废。抱冤泉壤。今此申奎复位论罪之疏。庶可申二百年冤郁之气。而朝议不一。又见废却。此岂国体事理之所安者耶。虽以历代已行之典言之。汉卫皇后见废于武帝。而宣帝即位。追复后号。晋王皇后见废于简文帝。而孝武即位。追尊位号。唐王皇后见废于玄宗。而代宗即位。追复后位。皇明胡皇后见废于宣宗。而英宗即位。亦追复后号。夫汉晋唐三后之追尊。未有何所据。而皇明胡皇后则虽曰宣宗终有悔心在。当时未及有处分。则亦不过为先帝之废后也。然英宗必复位而后已者。岂不以后之所坐。初非可废之罪。先帝本心。又不可不体之故耶。况皇明故事。自是我 朝时王之制。只依皇明已行之例。仰体 圣祖之本心。追伸慎氏之至冤。何害于处变礼之道。亦何悖于严出母之义耶。盖有罪之出母。固不复论矣。若夫无罪之出母。既出而或父有悔意。其出也或非父本心。则继先志而追正。亦人情天理之不可已
分。始于权奸为身之私计。指为邪论。沮复位之正议。由于两司执论之悖理。玆事首末。皆开群下。实非 圣祖之本心也。然而权奸则以覆载难容之罪。配食太庙。爵秩如旧。慎氏则以 圣祖元妃之尊。为群下所䝱废。抱冤泉壤。今此申奎复位论罪之疏。庶可申二百年冤郁之气。而朝议不一。又见废却。此岂国体事理之所安者耶。虽以历代已行之典言之。汉卫皇后见废于武帝。而宣帝即位。追复后号。晋王皇后见废于简文帝。而孝武即位。追尊位号。唐王皇后见废于玄宗。而代宗即位。追复后位。皇明胡皇后见废于宣宗。而英宗即位。亦追复后号。夫汉晋唐三后之追尊。未有何所据。而皇明胡皇后则虽曰宣宗终有悔心在。当时未及有处分。则亦不过为先帝之废后也。然英宗必复位而后已者。岂不以后之所坐。初非可废之罪。先帝本心。又不可不体之故耶。况皇明故事。自是我 朝时王之制。只依皇明已行之例。仰体 圣祖之本心。追伸慎氏之至冤。何害于处变礼之道。亦何悖于严出母之义耶。盖有罪之出母。固不复论矣。若夫无罪之出母。既出而或父有悔意。其出也或非父本心。则继先志而追正。亦人情天理之不可已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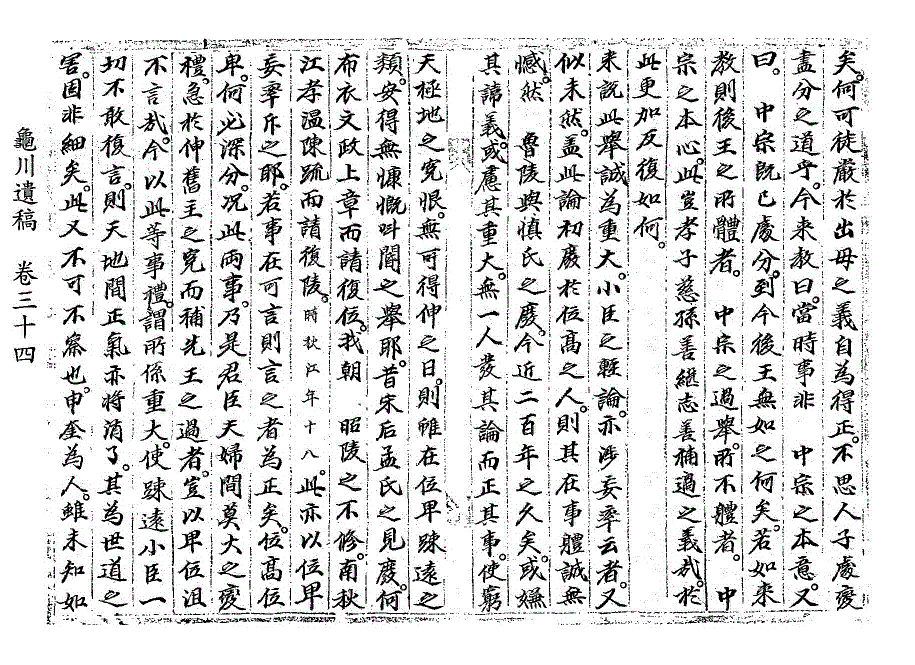 矣。何可徒严于出母之义自为得正。不思人子处变尽分之道乎。今来教曰。当时事非 中宗之本意。又曰。 中宗既已处分。到今后王无如之何矣。若如来教则后王之所体者。 中宗之过举。所不体者。 中宗之本心。此岂孝子慈孙善继志善补过之义哉。于此更加反复如何。
矣。何可徒严于出母之义自为得正。不思人子处变尽分之道乎。今来教曰。当时事非 中宗之本意。又曰。 中宗既已处分。到今后王无如之何矣。若如来教则后王之所体者。 中宗之过举。所不体者。 中宗之本心。此岂孝子慈孙善继志善补过之义哉。于此更加反复如何。来说此举诚为重大。小臣之轻论。亦涉妄率云者。又似未然。盖此论初废于位高之人。则其在事体诚无憾。然 鲁陵与慎氏之废。今近二百年之久矣。或嫌其讳义。或虑其重大。无一人发其论而正其事。使穷天极地之冤恨。无可得伸之日。则虽在位卑疏远之类。安得无慷慨叫阍之举耶。昔宋后孟氏之见废。何布衣文政上章而请复位。我朝 昭陵之不修。南秋江孝温陈疏而请复陵。(时秋江年十八。)此亦以位卑妄率斥之耶。若事在可言则言之者为正矣。位高位卑。何必深分。况此两事。乃是君臣夫妇间莫大之变礼。急于伸旧主之冤而补先王之过者。岂以卑位沮不言哉。今以此等事礼。谓所系重大。使疏远小臣一切不敢复言。则天地间正气亦将消了。其为世道之害。固非细矣。此又不可不察也。申奎为人。虽未知如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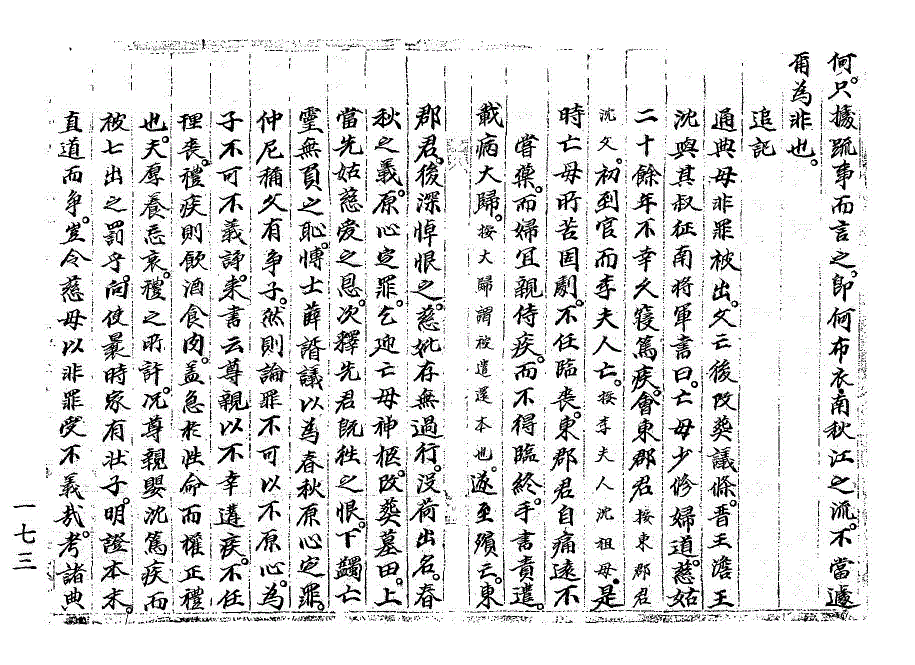 何。只据疏事而言之。即何布衣,南秋江之流。不当遽尔为非也。
何。只据疏事而言之。即何布衣,南秋江之流。不当遽尔为非也。追记
通典母非罪被出。父亡后改葬议条。晋王澹王沈与其叔征南将军书曰。亡母少修妇道。慈姑二十馀年不幸久寝笃疾。会东郡君(按东郡君沈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按李夫人沈祖母。)是时亡母所苦固剧。不任临丧。东郡君自痛远不 尝药。而妇宜亲侍疾。而不得临终。手书责遣。载病大归。(按大归谓被遣还本也。)遂至殡亡。东郡君。后深悼恨之。慈妣存无过行。没荷出名。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当先姑慈爱之恩。次释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灵无负之耻。博士薛谞议以为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称父有争子。然则论罪不可以不原心。为子不可不义诤。来书云尊亲以不幸遘疾。不任理丧。礼疾则饮酒食肉。盖急于性命而权正礼也。夫厚养忘哀。礼之所许。况尊亲婴沈笃疾而被七出之罚乎。向使曩时家有壮子。明證本末。直道而争。岂令慈母以非罪受不义哉。考诸典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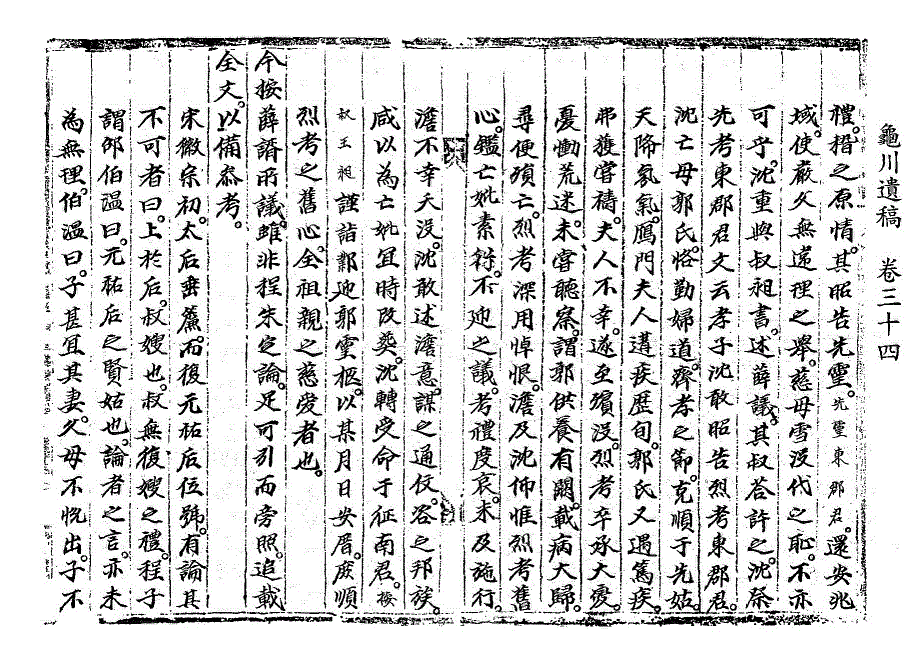 礼。稽之原情。其昭告先灵。(先灵东郡君。)还安兆域。使严父无违理之举。慈母雪没代之耻。不亦可乎。沈重与叔昶书。述薛议。其叔答许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云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妇道。齐孝之节。克顺于先姑。天降氛气。雁门夫人遘疾历旬。郭氏又遇笃疾。弗获尝祷。夫人不幸。遂至殡没。烈考卒承大变。忧恸荒迷。未尝听察。谓郭供养有阙。载病大归。寻便殒亡。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沈仰惟烈考旧心。鉴亡妣素行。不迎之议。考礼度哀。未及施行。澹不幸夭没。沈敢述澹意。谋之通伩。咨之邦族。咸以为亡妣宜时改葬。沈转受命于征南君。(按叔王昶)谨诣邺迎郭灵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顺烈考之旧心。全祖亲之慈爱者也。
礼。稽之原情。其昭告先灵。(先灵东郡君。)还安兆域。使严父无违理之举。慈母雪没代之耻。不亦可乎。沈重与叔昶书。述薛议。其叔答许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云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妇道。齐孝之节。克顺于先姑。天降氛气。雁门夫人遘疾历旬。郭氏又遇笃疾。弗获尝祷。夫人不幸。遂至殡没。烈考卒承大变。忧恸荒迷。未尝听察。谓郭供养有阙。载病大归。寻便殒亡。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沈仰惟烈考旧心。鉴亡妣素行。不迎之议。考礼度哀。未及施行。澹不幸夭没。沈敢述澹意。谋之通伩。咨之邦族。咸以为亡妣宜时改葬。沈转受命于征南君。(按叔王昶)谨诣邺迎郭灵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顺烈考之旧心。全祖亲之慈爱者也。今按薛谞所议。虽非程朱定论。足可引而旁照。追载全文。以备参考。
宋徽宗初。太后垂帘。而复元祐后位号。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于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程子谓邵伯温曰。元祐后之贤姑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4L 页
 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程子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程子喜曰。子之言得之矣。按孟氏之见废。本由于哲宗之自断。慎氏之见废。只出权奸之䝱请。两事曲折。迥然不同。若使程子当今日之议。则所以指疑如孟氏之事乎。抑别有道理而可以勘定者乎。
东平尉郑载崙。每以 鲁陵慎氏不得复位。私自慨叹。申奎即其相亲人。劝以呈疏。竟使 鲁陵得以复位。大抵此事。成于郑公之主张也。
明斋曰。当初糟糠云云之教。固见 圣心矣。至于朴金两贤疏留政院。及此是大事。岂可听小臣之言而为之乎之教。则人罕知之。今提起以明 圣心之所在极有力。甚幸甚幸。 圣心之有变于初。诚未可知也。
历代废后追复位号之事。无论其他。只皇明事。可据而遵行矣。其时廷议之不及于此何耶。岂有不同之曲折耶。今所论皆似精密。无任钦服钦服。
龟川先生遗稿卷之三十四 第 175H 页
 王沈之书。薛谞之议。今始得见。自古出母之事。如宋襄之河广。孔氏之不丧。盖严矣。若今以王沈之书。开其还复之门。则人子之于母。固至情所在。而后世之出妻者。岂皆以七去之罪耶。将无人不复而河广之义遂废矣。如此者。将何以防之。必有多少争端而不可止矣。如何。(以前书质之明斋。而所答如此。)
王沈之书。薛谞之议。今始得见。自古出母之事。如宋襄之河广。孔氏之不丧。盖严矣。若今以王沈之书。开其还复之门。则人子之于母。固至情所在。而后世之出妻者。岂皆以七去之罪耶。将无人不复而河广之义遂废矣。如此者。将何以防之。必有多少争端而不可止矣。如何。(以前书质之明斋。而所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