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安村集卷之三 第 x 页
安村集卷之三
杂著
杂著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0H 页
 手录
手录乙卯二月。始起攻尤斋之论。至有窜北移南之祸。凡欲附托时论者。毋论官与士。纷然而起。南天汉,李宇鼎,睦昌明倡之于前。赵师基,尹镌继之于后。此则在朝者主论也。都慎徵,郭世楗先于后。如洪天纪,朴㦥,朴凤祥辈。接迹而起。使一时善类斥逐殆尽。此则在野者附托而起也。甚至以议礼一说。欲钳制一时公论之人。可胜痛哉。可胜痛哉。
岁丙辰。得见许穆所制郑介清事迹。是欲崇奖介清。而不自知自欺而欺人也。介清以汝立逆党。谪死于宣庙朝。于今八十八年矣。穆之意。以为事在久远。人无耳闻而目睹者。若以其意恣加称誉。则可以掩一世耳目。而使介清为儒贤也。彼介清不过阿谀汝立。以汝立为见道高明者也。穆虽老妄失性之人。而犹有天赋之性。则岂不知排斥逆党之为可。而独能作文以虚褒者。是莫非党论之害也。穆乃善道之党也。善道一生事业。以侮辱松江。为发身之资。若以介清为逆党。则松江清白耿介之操。顾无以容喙。必以介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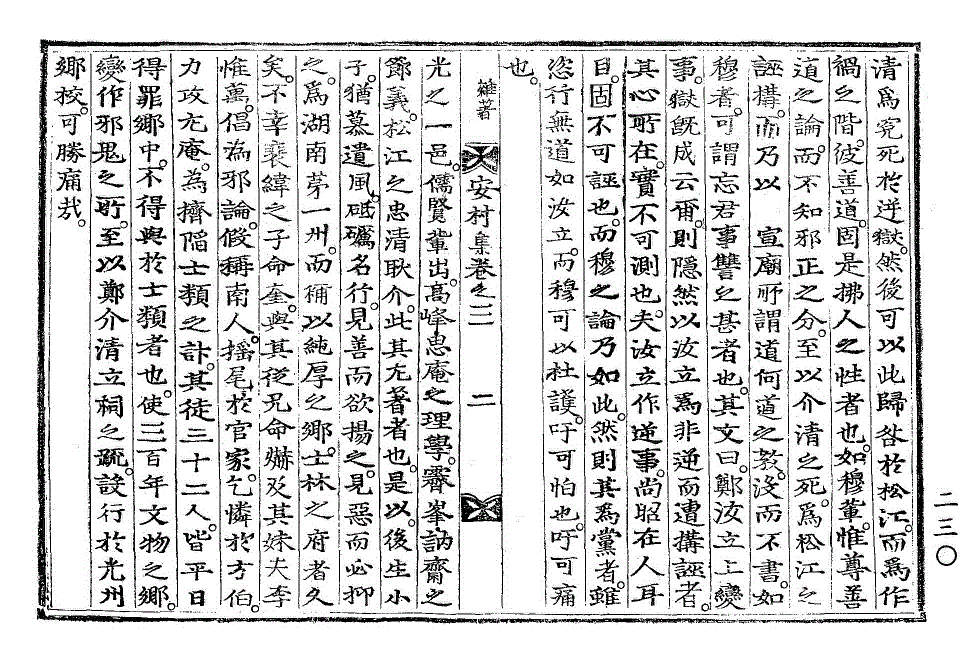 清为冤死于逆狱。然后可以此归咎于松江。而为作祸之阶。彼善道。固是拂人之性者也。如穆辈。惟尊善道之论。而不知邪正之分。至以介清之死。为松江之诬搆。而乃以 宣庙所谓道何道之教。没而不书。如穆者。可谓忘君事雠之甚者也。其文曰。郑汝立上变事。狱既成云尔。则隐然以汝立为非逆而遭搆诬者。其心所在。实不可测也。夫汝立作逆事。尚昭在人耳目。固不可诬也。而穆之论乃如此。然则其为党者。虽恣行无道如汝立。而穆可以杜护。吁可怕也。吁可痛也。
清为冤死于逆狱。然后可以此归咎于松江。而为作祸之阶。彼善道。固是拂人之性者也。如穆辈。惟尊善道之论。而不知邪正之分。至以介清之死。为松江之诬搆。而乃以 宣庙所谓道何道之教。没而不书。如穆者。可谓忘君事雠之甚者也。其文曰。郑汝立上变事。狱既成云尔。则隐然以汝立为非逆而遭搆诬者。其心所在。实不可测也。夫汝立作逆事。尚昭在人耳目。固不可诬也。而穆之论乃如此。然则其为党者。虽恣行无道如汝立。而穆可以杜护。吁可怕也。吁可痛也。光之一邑。儒贤辈出。高峰,思庵之理学。霁峰,讷斋之节义。松江之忠清耿介。此其尤著者也。是以。后生小子。犹慕遗风。砥砺名行。见善而欲扬之。见恶而必抑之。为湖南第一州。而称以纯厚之乡。士林之府者久矣。不幸裴纬之子命奎。与其从兄命赫及其妹夫李惟万。倡为邪论。假称南人。摇尾于官家。乞怜于方伯。力攻尤庵。为挤陷士类之计。其徒三十二人。皆平日得罪乡中。不得与于士类者也。使三百年文物之乡。变作邪鬼之所。至以郑介清立祠之疏。设行于光州乡校。可胜痛哉。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1H 页
 通道会所文。为伸正论。斥邪类事也。本邑之月峰书院。非我讷斋,思庵,高峰,沙溪,慎独斋诸老先生啜享之所耶。曩在邪类鸱张之日。乃敢以邪类之所自尊仰者谓之院长。而弁于儒籍之首。其为污浼儒林。亦已甚矣。况贼臣镌。斁绝伦纪。逆节已著。是所谓人得以诛之。而斯州之裴命奎,裴命赫,李惟桢,李惟万等。本以无识无赖之辈。见弃一乡。不齿士类。乃欲凭藉贼镌之势。以为渠发身之阶。遥附邪议。推为宗匠。跳踉欢呼。千丑百怪。固不可胜言。而尤可痛者。贼镌之徒。以瀗为名者。配于罗州。则幸其邻近递相往来。至相率运粮。以为贼瀗之资地。人之无良。胡至此极。噫。命赫等亦圆胪而横目。观其形则人也。而迹其所为。虽禽犊不如。资助贼瀗。以为附托贼镌之计。岂容以幺么至微而置而不论哉。玆于院籍中命赫等名字割出。以清儒籍。仍复通告于道内君子。以示其此辈有覆载难容之罪。不可以幺么至微而置之也。
通道会所文。为伸正论。斥邪类事也。本邑之月峰书院。非我讷斋,思庵,高峰,沙溪,慎独斋诸老先生啜享之所耶。曩在邪类鸱张之日。乃敢以邪类之所自尊仰者谓之院长。而弁于儒籍之首。其为污浼儒林。亦已甚矣。况贼臣镌。斁绝伦纪。逆节已著。是所谓人得以诛之。而斯州之裴命奎,裴命赫,李惟桢,李惟万等。本以无识无赖之辈。见弃一乡。不齿士类。乃欲凭藉贼镌之势。以为渠发身之阶。遥附邪议。推为宗匠。跳踉欢呼。千丑百怪。固不可胜言。而尤可痛者。贼镌之徒。以瀗为名者。配于罗州。则幸其邻近递相往来。至相率运粮。以为贼瀗之资地。人之无良。胡至此极。噫。命赫等亦圆胪而横目。观其形则人也。而迹其所为。虽禽犊不如。资助贼瀗。以为附托贼镌之计。岂容以幺么至微而置而不论哉。玆于院籍中命赫等名字割出。以清儒籍。仍复通告于道内君子。以示其此辈有覆载难容之罪。不可以幺么至微而置之也。李时文。乃故进士鼎新之子也。鼎新以丁巳榜进士。年至八十。别无毁誉于乡中。岁癸丑间。尤斋先生之两弟。为长城,淳昌倅。以鼎新为父同年。尽诚事之。知鼎新嗜酒。每送酒馔以候问。一时士人。皆以两倅为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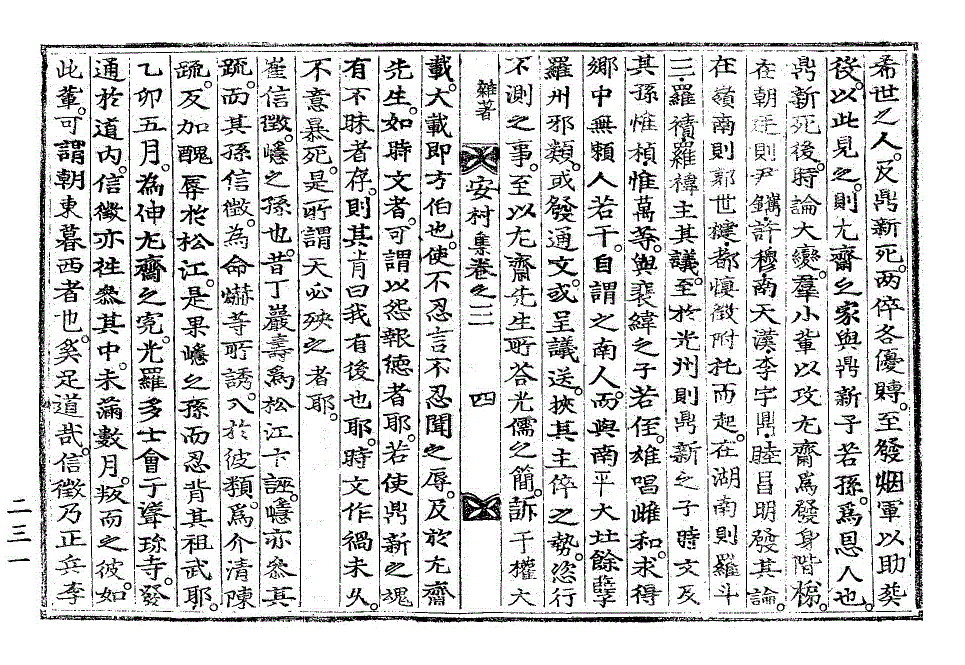 希世之人。及鼎新死。两倅各优赙。至发烟军以助葬役。以此见之。则尤斋之家与鼎新子若孙。为恩人也。鼎新死后。时论大变。群小辈以攻尤斋为发身阶梯。在朝廷则尹镌,许穆,南天汉,李宇鼎,睦昌明发其论。在岭南则郭世楗,都慎徵附托而起。在湖南则罗斗三,罗襀,罗袆主其议。至于光州则鼎新之子时文及其孙惟桢,惟万等。与裴纬之子若侄。雄唱雌和。求得乡中无赖人若干。自谓之南人。而与南平大北馀孽罗州邪类。或发通文。或呈议送。挟其主倅之势。恣行不测之事。至以尤斋先生所答光儒之简。诉于权大载。大载即方伯也。使不忍言不忍闻之辱。及于尤斋先生。如时文者。可谓以怨报德者耶。若使鼎新之魂有不昧者存。则其肯曰我有后也耶。时文作祸未久。不意暴死。是所谓天必殃之者耶。
希世之人。及鼎新死。两倅各优赙。至发烟军以助葬役。以此见之。则尤斋之家与鼎新子若孙。为恩人也。鼎新死后。时论大变。群小辈以攻尤斋为发身阶梯。在朝廷则尹镌,许穆,南天汉,李宇鼎,睦昌明发其论。在岭南则郭世楗,都慎徵附托而起。在湖南则罗斗三,罗襀,罗袆主其议。至于光州则鼎新之子时文及其孙惟桢,惟万等。与裴纬之子若侄。雄唱雌和。求得乡中无赖人若干。自谓之南人。而与南平大北馀孽罗州邪类。或发通文。或呈议送。挟其主倅之势。恣行不测之事。至以尤斋先生所答光儒之简。诉于权大载。大载即方伯也。使不忍言不忍闻之辱。及于尤斋先生。如时文者。可谓以怨报德者耶。若使鼎新之魂有不昧者存。则其肯曰我有后也耶。时文作祸未久。不意暴死。是所谓天必殃之者耶。崔信徵。嶾之孙也。昔丁岩寿为松江卞诬。嶾亦参其疏。而其孙信徵。为命赫等所诱。入于彼类。为介清陈疏。反加丑辱于松江。是果嶾之孙而忍背其祖武耶。乙卯五月。为伸尤斋之冤。光罗多士会于耸珍寺。发通于道内。信徵亦往参其中。未满数月。叛而之彼。如此辈。可谓朝东暮西者也。奚足道哉。信徵乃正兵李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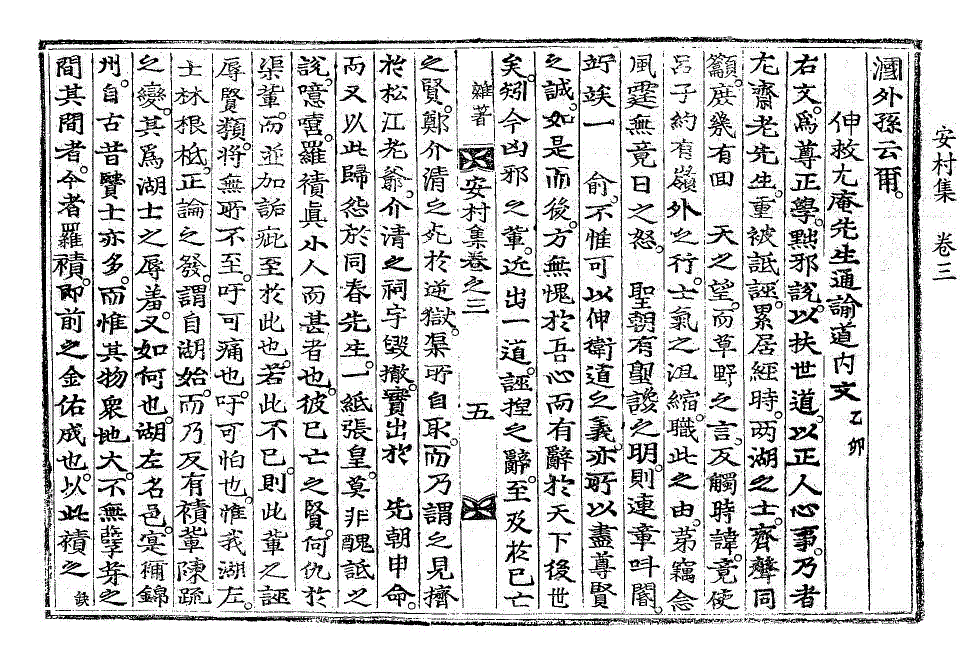 漍外孙云尔。
漍外孙云尔。伸救尤庵先生通谕道内文(乙卯)
右文。为尊正学。黜邪说。以扶世道。以正人心事。乃者尤斋老先生。重被诋诬。累居经时。两湖之士。齐声同吁。庶几有回 天之望。而草野之言。反触时讳。竟使吕子约有岭外之行。士气之沮缩。职此之由。第窃念风霆无竟日之怒。 圣朝有堲谗之明。则连章叫阍。伫俟一 俞。不惟可以伸卫道之义。亦所以尽尊贤之诚。如是而后。方无愧于吾心而有辞于天下后世矣。矧今凶邪之辈。近出一道。诬捏之辞。至及于已亡之贤。郑介清之死于逆狱。渠所自取。而乃谓之见挤于松江老爷。介清之祠宇毁撤。实出于 先朝申命。而又以此归怨于同春先生。一纸张皇。莫非丑诋之说。噫嘻。罗襀真小人而甚者也。彼已亡之贤。何仇于渠辈。而并加诟疵至于此也。若此不已。则此辈之诬辱贤类。将无所不至。吁可痛也。吁可怕也。惟我湖左。士林根柢。正论之发。谓自湖始。而乃反有襀辈陈疏之变。其为湖士之辱羞。又如何也。湖左名邑。寔称锦州。自古昔贤士亦多。而惟其物众地大。不无孽芽之间其间者。今者罗襀。即前之金佑成也。以此襀之(缺)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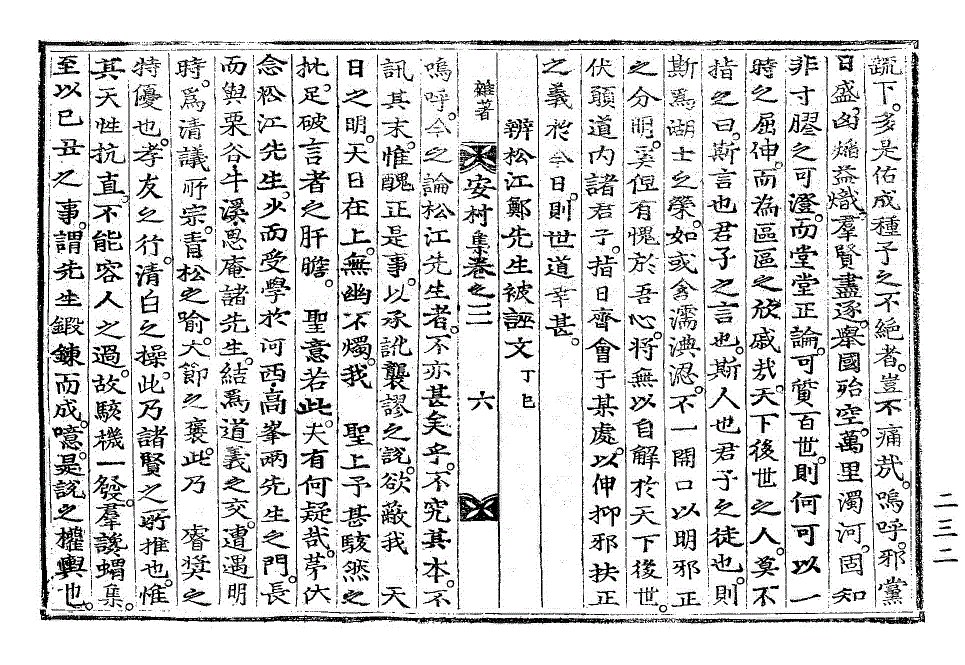 疏下。多是佑成种子之不绝者。岂不痛哉。呜呼。邪党日盛。凶焰益炽。群贤尽逐。举国殆空。万里浊河。固知非寸胶之可澄。而堂堂正论。可质百世。则何可以一时之屈伸。而为区区之欣戚哉。天下后世之人。莫不指之曰。斯言也君子之言也。斯人也君子之徒也。则斯为湖士之荣。如或含濡淟涊。不一开口以明邪正之分明。奚但有愧于吾心。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伏愿道内诸君子。指日齐会于某处。以伸抑邪扶正之义于今日。则世道幸甚。
疏下。多是佑成种子之不绝者。岂不痛哉。呜呼。邪党日盛。凶焰益炽。群贤尽逐。举国殆空。万里浊河。固知非寸胶之可澄。而堂堂正论。可质百世。则何可以一时之屈伸。而为区区之欣戚哉。天下后世之人。莫不指之曰。斯言也君子之言也。斯人也君子之徒也。则斯为湖士之荣。如或含濡淟涊。不一开口以明邪正之分明。奚但有愧于吾心。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伏愿道内诸君子。指日齐会于某处。以伸抑邪扶正之义于今日。则世道幸甚。辨松江郑先生被诬文(丁巳)
呜呼。今之论松江先生者。不亦甚矣乎。不究其本。不讯其末。惟丑正是事。以承讹袭谬之说。欲蔽我 天日之明。天日在上。无幽不烛。我 圣上予甚骇然之批。足破言者之肝胆。 圣意若此。夫有何疑哉。第伏念松江先生。少而受学于河西,高峰两先生之门。长而与栗谷,牛溪,思庵诸先生。结为道义之交。遭遇明时。为清议所宗。青松之喻。大节之褒。此乃 睿奖之特优也。孝友之行。清白之操。此乃诸贤之所推也。惟其天性抗直。不能容人之过。故骇机一发。群谗猬集。至以己丑之事。谓先生锻鍊而成。噫。是说之权舆也。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3H 页
 非仁弘辈之倡之于前。而尔瞻徒之继之于后乎。昔在辛卯春。媒孽先生者。至密且细。西塞之窜。无非谗者之效。而无敢以治狱之说。加之于先生者。盖以治狱不久而文案具在。虽以三尺之喙。亦不得诪张之矣。及其壬辰之后。知国书为兵燹烧尽。闯然为嫁祸之计。而犹不敢肆然作说矣。至昏朝人文已晦。仁弘,尔瞻。寔繁其徒。如金佑成辈。日以攻先生为发身之阶。掉舌翻唇。钩成齮龁之祸。自是之后。人各增其言。岁辄加其说。终乃以辛卯夏秋间就死之人。亦谓之死于先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者也。先生之递委官。在于辛卯二月。国乘野录。尚班班可考。则虽欲诬之。其可得乎。先生之在委官也。人之就理者。苟有一毫可恕之冤。则或书启而救之。或面对而解之。或并与其人之所不能自对者而论释备至。则可见大君子秉心之公也。初以为恩。而送子而候于栫棘者。终亦为雠。而随而媒孽之。恩雠倒置。岂理也哉。况其时出入委官之列者有二三大臣。而坐视蔓延之患。无一言平反。毕竟搆捏之惨。不归于彼而在于此。其亦异哉。逮我 仁庙改玉之初。明命赫然。群枉毕伸。昔之攻先生以为利者。皆蒙显戮。公论之定。不待
非仁弘辈之倡之于前。而尔瞻徒之继之于后乎。昔在辛卯春。媒孽先生者。至密且细。西塞之窜。无非谗者之效。而无敢以治狱之说。加之于先生者。盖以治狱不久而文案具在。虽以三尺之喙。亦不得诪张之矣。及其壬辰之后。知国书为兵燹烧尽。闯然为嫁祸之计。而犹不敢肆然作说矣。至昏朝人文已晦。仁弘,尔瞻。寔繁其徒。如金佑成辈。日以攻先生为发身之阶。掉舌翻唇。钩成齮龁之祸。自是之后。人各增其言。岁辄加其说。终乃以辛卯夏秋间就死之人。亦谓之死于先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者也。先生之递委官。在于辛卯二月。国乘野录。尚班班可考。则虽欲诬之。其可得乎。先生之在委官也。人之就理者。苟有一毫可恕之冤。则或书启而救之。或面对而解之。或并与其人之所不能自对者而论释备至。则可见大君子秉心之公也。初以为恩。而送子而候于栫棘者。终亦为雠。而随而媒孽之。恩雠倒置。岂理也哉。况其时出入委官之列者有二三大臣。而坐视蔓延之患。无一言平反。毕竟搆捏之惨。不归于彼而在于此。其亦异哉。逮我 仁庙改玉之初。明命赫然。群枉毕伸。昔之攻先生以为利者。皆蒙显戮。公论之定。不待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3L 页
 百年。而荣爵之恩。及于泉壤。一国之士气。欣欣然相庆曰。凶秽之徒。既尽伏其辜矣。今以后虽千百岁。宁复有如仁弘,尔瞻,佑成者辈哉。不料今者杨梦举等。敢以仁弘,尔瞻,佑成等之馀论。肆然聚其党。封章而达于 天。是岂忍为之者耶。彼梦举等多人。岂尽无人心哉。犹袭凶秽之论。以自陷于千古罪臼。其亦可哀也已。我 圣上一言挥斥。明示好恶。则今虽欲辨其诬。似无可措说者矣。然念此事首末。远在八十年前。若不举其实一陈于 天聪。则九重深邃。亦何以备知受诬之至此乎。况我一道内先辈。虽在祸机方张之日。而犹奋然而起。不顾祸福。而为先生必欲伸卞者。其意岂偶然哉。盖以不如是。则吾儒者正气。不得塞于天地之间矣。况今 圣明在上。其忍无一言以助我 圣德烛幽之明也哉。此生等之所以愿与诸君子封章陈卞。以斥夫丑诋者诬罔之说也。一道内持正论之士。其意岂有异于生等乎。惟愿以四月十五日。会于长城。与之相议。因为拜疏叫 阍。则庶或不愧于先辈正大之论矣。深幸诸君子之谅此而有济济之美也。
百年。而荣爵之恩。及于泉壤。一国之士气。欣欣然相庆曰。凶秽之徒。既尽伏其辜矣。今以后虽千百岁。宁复有如仁弘,尔瞻,佑成者辈哉。不料今者杨梦举等。敢以仁弘,尔瞻,佑成等之馀论。肆然聚其党。封章而达于 天。是岂忍为之者耶。彼梦举等多人。岂尽无人心哉。犹袭凶秽之论。以自陷于千古罪臼。其亦可哀也已。我 圣上一言挥斥。明示好恶。则今虽欲辨其诬。似无可措说者矣。然念此事首末。远在八十年前。若不举其实一陈于 天聪。则九重深邃。亦何以备知受诬之至此乎。况我一道内先辈。虽在祸机方张之日。而犹奋然而起。不顾祸福。而为先生必欲伸卞者。其意岂偶然哉。盖以不如是。则吾儒者正气。不得塞于天地之间矣。况今 圣明在上。其忍无一言以助我 圣德烛幽之明也哉。此生等之所以愿与诸君子封章陈卞。以斥夫丑诋者诬罔之说也。一道内持正论之士。其意岂有异于生等乎。惟愿以四月十五日。会于长城。与之相议。因为拜疏叫 阍。则庶或不愧于先辈正大之论矣。深幸诸君子之谅此而有济济之美也。安村集卷之三
语录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4H 页
 蓬海录
蓬海录丁巳九月二十七日。与高斗经,柳汉徵,柳应寿,三从弟光一同行。十月十一日。到长鬐县。寻先生谪庐。两三茅屋。依在山下。中有稍大一家。以山竹作编为篱。高可三四丈。南有一小门。仅仅出入。人闻先生在此荆棘中。益不堪伤时之痛。仍到邑之东一村。得占所寓之家。然后吾五人连袂步行。至于棘门外。使所带奴招得应门之童。使之通刺于先生前。俄有一少儒自棘里而出。引我辈至一空舍。乃本县禀官家云。少儒即先生之孙畴锡也。形容端正。行止安详。可知为先生长者门下人。问先生安否。相与语。少顷。少儒还入于棘里。以告吾辈必欲进拜之意。先生乃令少儒传辞于吾辈曰。闻跋涉远来。慰喜且感。即欲相见。而所入来穴门至小且高。不敢请客而入云云。吾五人即与少儒同入棘门之内。有大杏树立在门内。可作坛盘旋。其下有竹床二。一高而一低。意者先生避暑于此。诸门生或且讲业也。围篱内。有三间厅堂颇精洒。又其内有三间屋。二间房。一间竹床。即先生所寓之室也。吾五人并入参拜。则先生手小竹杖。迎我辈于房中。逢迎之喜。蔼然可掬。叙暄凉毕。以诸友及吾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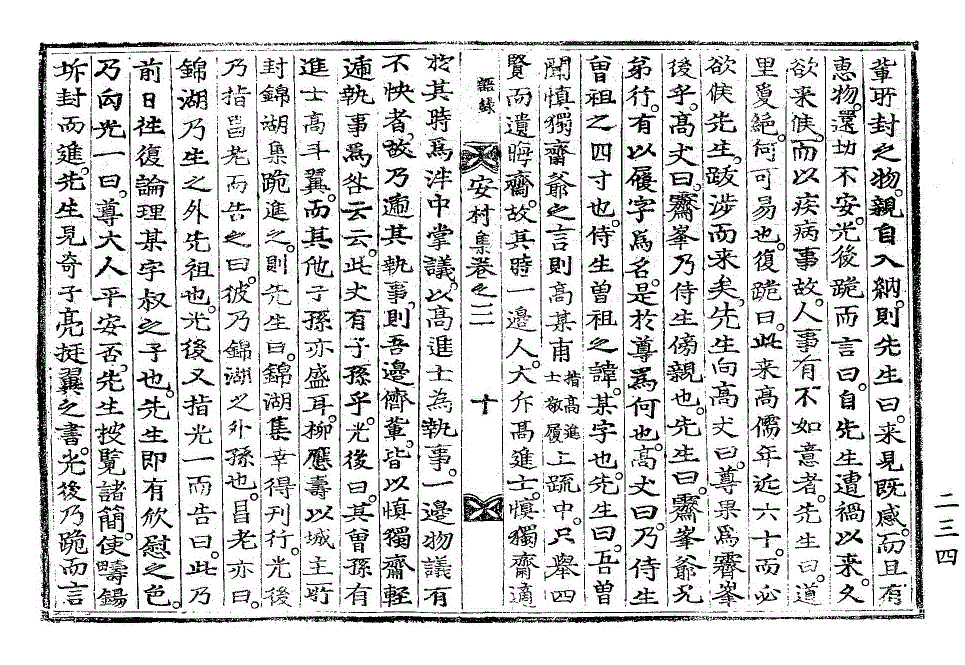 辈所封之物。亲自入纳。则先生曰。来见既感。而且有惠物。还切不安。光后跪而言曰。自先生遭祸以来。久欲来候。而以疾病事故。人事有不如意者。先生曰。道里夐绝。何可易也。复跪曰。此来高儒年近六十。而必欲候先生。跋涉而来矣。先生向高丈曰。尊果为霁峰后乎。高丈曰。霁峰乃侍生傍亲也。先生曰。霁峰爷兄弟行。有以履字为名。是于尊为何也。高丈曰。乃侍生曾祖之四寸也。侍生曾祖之讳。某字也。先生曰。吾曾闻慎独斋爷之言则高某甫(指高进士敬履)上疏中。只举四贤而遗晦斋。故其时一边人。大斥高进士。慎独斋适于其时为泮中掌议。以高进士为执事。一边物议有不怏者。故乃递其执事。则吾边侪辈。皆以慎独斋轻递执事为咎云云。此丈有子孙乎。光后曰。其曾孙有进士高斗翼。而其他子孙亦盛耳。柳应寿以城主所封锦湖集跪进之。则先生曰。锦湖集幸得刊行。光后乃指昌老而告之曰。彼乃锦湖之外孙也。昌老亦曰。锦湖乃生之外先祖也。光后又指光一而告曰。此乃前日往复论理某字叔之子也。先生即有欣慰之色。乃向光一曰。尊大人平安否。先生披览诸简。使畴锡坼封而进。先生见奇子亮挺翼之书。光后乃跪而言
辈所封之物。亲自入纳。则先生曰。来见既感。而且有惠物。还切不安。光后跪而言曰。自先生遭祸以来。久欲来候。而以疾病事故。人事有不如意者。先生曰。道里夐绝。何可易也。复跪曰。此来高儒年近六十。而必欲候先生。跋涉而来矣。先生向高丈曰。尊果为霁峰后乎。高丈曰。霁峰乃侍生傍亲也。先生曰。霁峰爷兄弟行。有以履字为名。是于尊为何也。高丈曰。乃侍生曾祖之四寸也。侍生曾祖之讳。某字也。先生曰。吾曾闻慎独斋爷之言则高某甫(指高进士敬履)上疏中。只举四贤而遗晦斋。故其时一边人。大斥高进士。慎独斋适于其时为泮中掌议。以高进士为执事。一边物议有不怏者。故乃递其执事。则吾边侪辈。皆以慎独斋轻递执事为咎云云。此丈有子孙乎。光后曰。其曾孙有进士高斗翼。而其他子孙亦盛耳。柳应寿以城主所封锦湖集跪进之。则先生曰。锦湖集幸得刊行。光后乃指昌老而告之曰。彼乃锦湖之外孙也。昌老亦曰。锦湖乃生之外先祖也。光后又指光一而告曰。此乃前日往复论理某字叔之子也。先生即有欣慰之色。乃向光一曰。尊大人平安否。先生披览诸简。使畴锡坼封而进。先生见奇子亮挺翼之书。光后乃跪而言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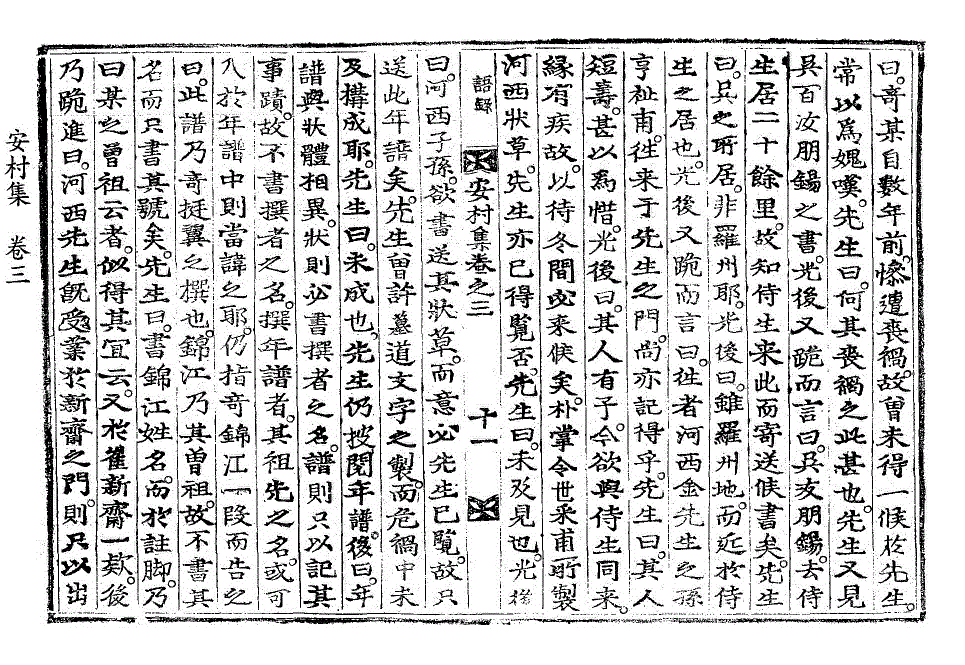 曰。奇某自数年前。惨遭丧祸。故曾未得一候于先生。常以为愧叹。先生曰。何其丧祸之此甚也。先生又见吴百汝朋锡之书。光后又跪而言曰。吴友朋锡。去侍生居二十馀里。故知侍生来此而寄送候书矣。先生曰。吴之所居。非罗州耶。光后曰。虽罗州地。而近于侍生之居也。光后又跪而言曰。往者河西金先生之孙亨祉甫。往来于先生之门。尚亦记得乎。先生曰。其人短寿。甚以为惜。光后曰。其人有子。今欲与侍生同来。缘有疾故。以待冬间必来候矣。朴掌令世采甫所制河西状草。先生亦已得览否。先生曰。未及见也。光后曰。河西子孙。欲书送其状草。而意必先生已览。故只送此年谱矣。先生曾许墓道文字之制。而危祸中未及搆成耶。先生曰。未成也。先生仍披阅年谱。后曰。年谱与状体相异。状则必书撰者之名。谱则只以记其事迹。故不书撰者之名。撰年谱者。其祖先之名。或可入于年谱中则当讳之耶。仍指奇锦江一段而告之曰。此谱乃奇挺翼之撰也。锦江乃其曾祖。故不书其名而只书其号矣。先生曰。书锦江姓名。而于注脚。乃曰某之曾祖云者。似得其宜云。又于崔新斋一款。后乃跪进曰。河西先生既受业于新斋之门。则只以出
曰。奇某自数年前。惨遭丧祸。故曾未得一候于先生。常以为愧叹。先生曰。何其丧祸之此甚也。先生又见吴百汝朋锡之书。光后又跪而言曰。吴友朋锡。去侍生居二十馀里。故知侍生来此而寄送候书矣。先生曰。吴之所居。非罗州耶。光后曰。虽罗州地。而近于侍生之居也。光后又跪而言曰。往者河西金先生之孙亨祉甫。往来于先生之门。尚亦记得乎。先生曰。其人短寿。甚以为惜。光后曰。其人有子。今欲与侍生同来。缘有疾故。以待冬间必来候矣。朴掌令世采甫所制河西状草。先生亦已得览否。先生曰。未及见也。光后曰。河西子孙。欲书送其状草。而意必先生已览。故只送此年谱矣。先生曾许墓道文字之制。而危祸中未及搆成耶。先生曰。未成也。先生仍披阅年谱。后曰。年谱与状体相异。状则必书撰者之名。谱则只以记其事迹。故不书撰者之名。撰年谱者。其祖先之名。或可入于年谱中则当讳之耶。仍指奇锦江一段而告之曰。此谱乃奇挺翼之撰也。锦江乃其曾祖。故不书其名而只书其号矣。先生曰。书锦江姓名。而于注脚。乃曰某之曾祖云者。似得其宜云。又于崔新斋一款。后乃跪进曰。河西先生既受业于新斋之门。则只以出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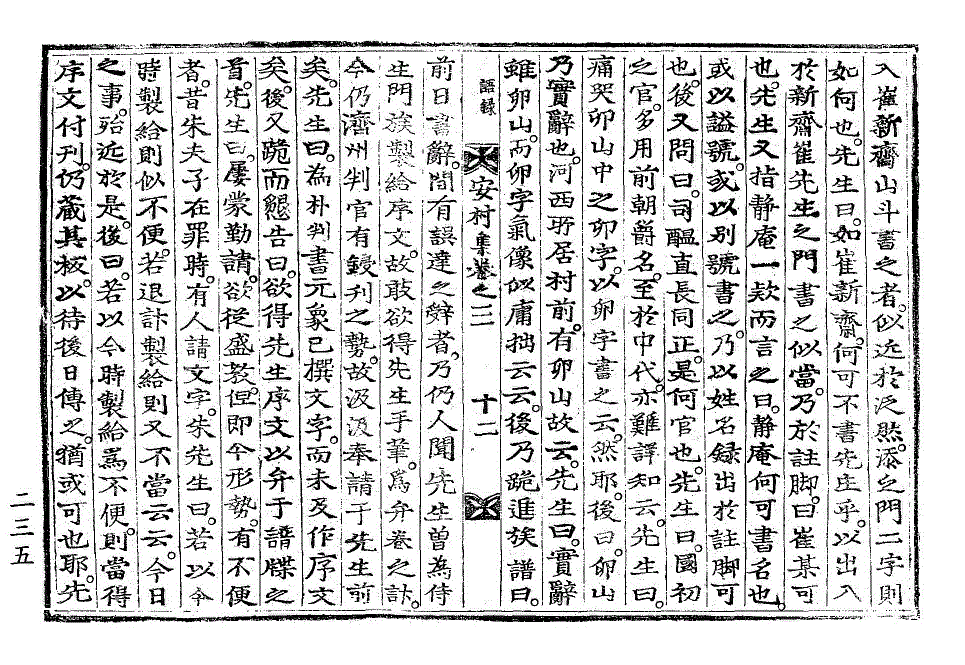 入崔新斋山斗书之者。似近于泛然。添之门二字则如何也。先生曰。如崔新斋。何可不书先生乎。以出入于新斋崔先生之门书之似当。乃于注脚。曰崔某可也。先生又指静庵一款而言之曰。静庵何可书名也。或以谥号。或以别号书之。乃以姓名录出于注脚可也。后又问曰。司酝直长同正。是何官也。先生曰。国初之官。多用前朝爵名。至于中代。亦难详知云。先生曰。痛哭卯山中之卯字。以卵字书之云。然耶。后曰。卵山乃实辞也。河西所居村前。有卵山故云。先生曰。实辞虽卵山。而卵字气像似庸拙云云。后乃跪进族谱曰。前日书辞。间有误达之辞者。乃仍人闻先生曾为侍生门族制给序文。故敢欲得先生手笔。为弁卷之计。今仍济州判官有锓刊之势。故汲汲奉请于先生前矣。先生曰。为朴判书元象已撰文字。而未及作序文矣。后又跪而恳告曰。欲得先生序文以弁于谱牒之首。先生曰。屡蒙勤请。欲从盛教。但即今形势。有不便者。昔朱夫子在罪时。有人请文字。朱先生曰。若以今时制给则似不便。若退计制给则又不当云云。今日之事。殆近于是。后曰。若以今时制给为不便。则当得序文付刊。仍藏其板。以待后日传之。犹或可也耶。先
入崔新斋山斗书之者。似近于泛然。添之门二字则如何也。先生曰。如崔新斋。何可不书先生乎。以出入于新斋崔先生之门书之似当。乃于注脚。曰崔某可也。先生又指静庵一款而言之曰。静庵何可书名也。或以谥号。或以别号书之。乃以姓名录出于注脚可也。后又问曰。司酝直长同正。是何官也。先生曰。国初之官。多用前朝爵名。至于中代。亦难详知云。先生曰。痛哭卯山中之卯字。以卵字书之云。然耶。后曰。卵山乃实辞也。河西所居村前。有卵山故云。先生曰。实辞虽卵山。而卵字气像似庸拙云云。后乃跪进族谱曰。前日书辞。间有误达之辞者。乃仍人闻先生曾为侍生门族制给序文。故敢欲得先生手笔。为弁卷之计。今仍济州判官有锓刊之势。故汲汲奉请于先生前矣。先生曰。为朴判书元象已撰文字。而未及作序文矣。后又跪而恳告曰。欲得先生序文以弁于谱牒之首。先生曰。屡蒙勤请。欲从盛教。但即今形势。有不便者。昔朱夫子在罪时。有人请文字。朱先生曰。若以今时制给则似不便。若退计制给则又不当云云。今日之事。殆近于是。后曰。若以今时制给为不便。则当得序文付刊。仍藏其板。以待后日传之。犹或可也耶。先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6H 页
 生笑。曰退计而制给既不当。则留时而传之。其可乎哉。然朱夫子制给陈俊卿之状。考其时则极遭危祸时也。然则朱夫子亦或制之矣。后乃欣然更进曰。请得如陈俊卿之状。先生之意。似将许制矣。日已暮矣。将告退于主人家。后乃跪言曰。侍生等不远千里而来者。必欲侍先生也。若以出入棘里。添今日之祸。则侍生等何敢请之乎。若不尔则侍生请连日出入以侍先生也。先生曰。此亦势也。往者或人来见。而不敢入棘门。吾或立见于门内。向日李监司䎘,李兵使重臣。不意驰来。不通于内。率尔入来。自是之后。外人之来见者。不忌入此门。吾亦无禁惮之心。后曰。然则侍生当连日入来矣。遂退宿于主人家。十二日。促饭而齐进。暂休于外舍。与宋畴锡,晦锡兄弟及周希濂相话。俄而使一小婢。促令延客而入。吾五人以畴锡为前导而进候于先生。后曰。夜来痔疾何如。先生曰。苦歇无常。非朝夕可差之疾。后曰。已成肿乎。先生曰。此疾之根已久。而及其成浓之后始知之。柳汉徵叔起曰。人言此疾乃寿證也。先生初以水疾误听而曰。乃湿症也。后曰。非水疾也。乃长寿之證云。先生微哂曰。即今七十。既为长寿。更何望哉。后乃以牧使所赠诗
生笑。曰退计而制给既不当。则留时而传之。其可乎哉。然朱夫子制给陈俊卿之状。考其时则极遭危祸时也。然则朱夫子亦或制之矣。后乃欣然更进曰。请得如陈俊卿之状。先生之意。似将许制矣。日已暮矣。将告退于主人家。后乃跪言曰。侍生等不远千里而来者。必欲侍先生也。若以出入棘里。添今日之祸。则侍生等何敢请之乎。若不尔则侍生请连日出入以侍先生也。先生曰。此亦势也。往者或人来见。而不敢入棘门。吾或立见于门内。向日李监司䎘,李兵使重臣。不意驰来。不通于内。率尔入来。自是之后。外人之来见者。不忌入此门。吾亦无禁惮之心。后曰。然则侍生当连日入来矣。遂退宿于主人家。十二日。促饭而齐进。暂休于外舍。与宋畴锡,晦锡兄弟及周希濂相话。俄而使一小婢。促令延客而入。吾五人以畴锡为前导而进候于先生。后曰。夜来痔疾何如。先生曰。苦歇无常。非朝夕可差之疾。后曰。已成肿乎。先生曰。此疾之根已久。而及其成浓之后始知之。柳汉徵叔起曰。人言此疾乃寿證也。先生初以水疾误听而曰。乃湿症也。后曰。非水疾也。乃长寿之證云。先生微哂曰。即今七十。既为长寿。更何望哉。后乃以牧使所赠诗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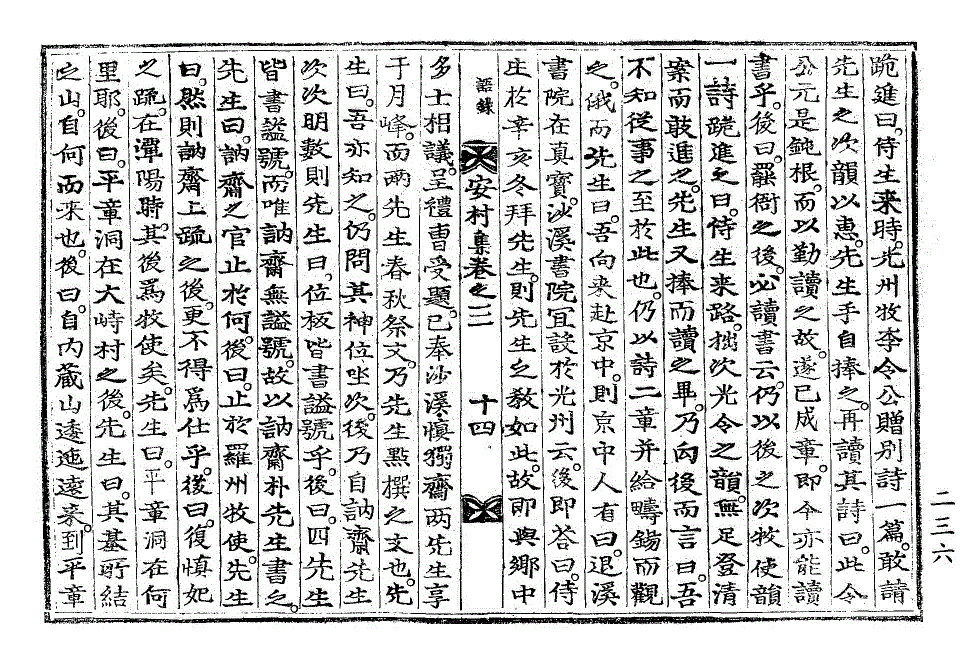 跪进曰。侍生来时。光州牧李令公赠别诗一篇。敢请先生之次韵以惠。先生手自捧之。再读其诗曰。此令公元是钝根。而以勤读之故。遂已成章。即今亦能读书乎。后曰。罢衙之后。必读书云。仍以后之次牧使韵一诗跪进之曰。侍生来路。拙次光令之韵。无足登清案而敢进之。先生又捧而读之毕。乃向后而言曰。吾不知从事之至于此也。仍以诗二章并给畴锡而观之。俄而先生曰。吾向来赴京中。则京中人有曰。退溪书院在真宝。沙溪书院宜设于光州云。后即答曰。侍生于辛亥冬拜先生。则先生之教如此。故即与乡中多士相议。呈礼曹受题。已奉沙溪,慎独斋两先生享于月峰。而两先生春秋祭文。乃先生点撰之文也。先生曰。吾亦知之。仍问其神位坐次。后乃自讷斋先生次次明数则先生曰。位板皆书谥号乎。后曰。四先生皆书谥号。而唯讷斋无谥号。故以讷斋朴先生书之。先生曰。讷斋之官止于何。后曰。止于罗州牧使。先生曰。然则讷斋上疏之后。更不得为仕乎。后曰。复慎妃之疏。在潭阳时。其后为牧使矣。先生曰。平章洞在何里耶。后曰。平章洞在大峙村之后。先生曰。其基所结之山。自何而来也。后曰。自内藏山逶迤远来。到平章
跪进曰。侍生来时。光州牧李令公赠别诗一篇。敢请先生之次韵以惠。先生手自捧之。再读其诗曰。此令公元是钝根。而以勤读之故。遂已成章。即今亦能读书乎。后曰。罢衙之后。必读书云。仍以后之次牧使韵一诗跪进之曰。侍生来路。拙次光令之韵。无足登清案而敢进之。先生又捧而读之毕。乃向后而言曰。吾不知从事之至于此也。仍以诗二章并给畴锡而观之。俄而先生曰。吾向来赴京中。则京中人有曰。退溪书院在真宝。沙溪书院宜设于光州云。后即答曰。侍生于辛亥冬拜先生。则先生之教如此。故即与乡中多士相议。呈礼曹受题。已奉沙溪,慎独斋两先生享于月峰。而两先生春秋祭文。乃先生点撰之文也。先生曰。吾亦知之。仍问其神位坐次。后乃自讷斋先生次次明数则先生曰。位板皆书谥号乎。后曰。四先生皆书谥号。而唯讷斋无谥号。故以讷斋朴先生书之。先生曰。讷斋之官止于何。后曰。止于罗州牧使。先生曰。然则讷斋上疏之后。更不得为仕乎。后曰。复慎妃之疏。在潭阳时。其后为牧使矣。先生曰。平章洞在何里耶。后曰。平章洞在大峙村之后。先生曰。其基所结之山。自何而来也。后曰。自内藏山逶迤远来。到平章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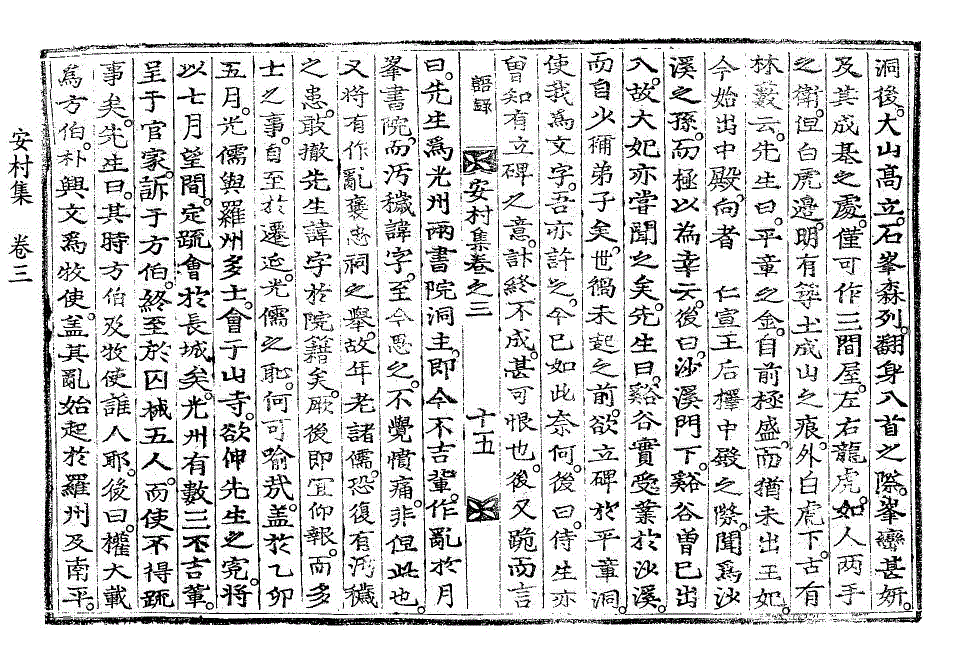 洞后。大山高立。石峰森列。翻身入首之际。峰峦甚妍。及其成基之处。仅可作三间屋。左右龙虎。如人两手之卫。但白虎边。明有筑土成山之痕。外白虎下。古有林薮云。先生曰。平章之金。自前极盛。而犹未出王妃。今始出中殿。向者 仁宣王后择中殿之际。闻为沙溪之孙。而极以为幸云。后曰。沙溪门下。溪谷曾已出入。故大妃亦尝闻之矣。先生曰。溪谷实受业于沙溪。而自少称弟子矣。世祸未起之前。欲立碑于平章洞。使我为文字。吾亦许之。今已如此奈何。后曰。侍生亦曾知有立碑之意。计终不成。甚可恨也。后又跪而言曰。先生为光州两书院洞主。即今不吉辈。作乱于月峰书院。而污秽讳字。至今思之。不觉愤痛。非但此也。又将有作乱褒忠祠之举。故年老诸儒。恐复有污秽之患。敢撤先生讳字于院籍矣。厥后即宜仰报。而多士之事。自至于迁延。光儒之耻。何可喻哉。盖于乙卯五月。光儒与罗州多士。会于山寺。欲伸先生之冤。将以七月望间。定疏会于长城矣。光州有数三不吉辈。呈于官家。诉于方伯。终至于囚械五人。而使不得疏事矣。先生曰。其时方伯及牧使谁人耶。后曰。权大载为方伯。朴兴文为牧使。盖其乱始起于罗州及南平。
洞后。大山高立。石峰森列。翻身入首之际。峰峦甚妍。及其成基之处。仅可作三间屋。左右龙虎。如人两手之卫。但白虎边。明有筑土成山之痕。外白虎下。古有林薮云。先生曰。平章之金。自前极盛。而犹未出王妃。今始出中殿。向者 仁宣王后择中殿之际。闻为沙溪之孙。而极以为幸云。后曰。沙溪门下。溪谷曾已出入。故大妃亦尝闻之矣。先生曰。溪谷实受业于沙溪。而自少称弟子矣。世祸未起之前。欲立碑于平章洞。使我为文字。吾亦许之。今已如此奈何。后曰。侍生亦曾知有立碑之意。计终不成。甚可恨也。后又跪而言曰。先生为光州两书院洞主。即今不吉辈。作乱于月峰书院。而污秽讳字。至今思之。不觉愤痛。非但此也。又将有作乱褒忠祠之举。故年老诸儒。恐复有污秽之患。敢撤先生讳字于院籍矣。厥后即宜仰报。而多士之事。自至于迁延。光儒之耻。何可喻哉。盖于乙卯五月。光儒与罗州多士。会于山寺。欲伸先生之冤。将以七月望间。定疏会于长城矣。光州有数三不吉辈。呈于官家。诉于方伯。终至于囚械五人。而使不得疏事矣。先生曰。其时方伯及牧使谁人耶。后曰。权大载为方伯。朴兴文为牧使。盖其乱始起于罗州及南平。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7L 页
 有若干大北之后。送通于光州。而语极凶悖。侍生等七十馀人。适会于乡校。不忍见贼孽辈通文来到公会。即令烧火。凶辈以焚通为执言而治之甚毒。侍生与柳应寿则以攻斥大北之后。至受笞五十之刑矣。先生酸鼻惊慄曰。何其甚耶。后曰。若以法论之则方伯,守令。何可加笞于侍生。而近日之官。蔑法恣行。是所愤也。先生曰。生进何可加笞乎。即今方伯为谁也。黄教官其终免杖耶。后曰。方伯报于朝廷。而朝廷不为深治。朴信圭亦不无无聊之心。以此止其杖云矣。先生曰。唯唯。后又跪而进曰。今年六月得地师。往见李泼先代之坟。有李达善墓碑。外面即尹衢之文而李山海书之。阴有栗谷先生志文。不过五六行。而其字画似是栗谷亲笔。先生曰。栗谷之笔。虽非有名。而端正可爱。李达善于李泼。为几代祖耶。高丈即对曰。李泼之曾祖也。后曰。闻朴掌令世采甫,李三陟选甫。有收拾栗谷遗文之事。即誊送于李三陟家矣。先生曰。果有收聚之事矣。完南为光牧时。尊与李选相见乎。后曰。完南为光牧时。是侍生幼少时也。何可及见乎。中年游洛时。与之相知耳。先生曰。栗谷先生。初与李泼相亲。为共济国事计也。重峰元是泼党。而终至
有若干大北之后。送通于光州。而语极凶悖。侍生等七十馀人。适会于乡校。不忍见贼孽辈通文来到公会。即令烧火。凶辈以焚通为执言而治之甚毒。侍生与柳应寿则以攻斥大北之后。至受笞五十之刑矣。先生酸鼻惊慄曰。何其甚耶。后曰。若以法论之则方伯,守令。何可加笞于侍生。而近日之官。蔑法恣行。是所愤也。先生曰。生进何可加笞乎。即今方伯为谁也。黄教官其终免杖耶。后曰。方伯报于朝廷。而朝廷不为深治。朴信圭亦不无无聊之心。以此止其杖云矣。先生曰。唯唯。后又跪而进曰。今年六月得地师。往见李泼先代之坟。有李达善墓碑。外面即尹衢之文而李山海书之。阴有栗谷先生志文。不过五六行。而其字画似是栗谷亲笔。先生曰。栗谷之笔。虽非有名。而端正可爱。李达善于李泼。为几代祖耶。高丈即对曰。李泼之曾祖也。后曰。闻朴掌令世采甫,李三陟选甫。有收拾栗谷遗文之事。即誊送于李三陟家矣。先生曰。果有收聚之事矣。完南为光牧时。尊与李选相见乎。后曰。完南为光牧时。是侍生幼少时也。何可及见乎。中年游洛时。与之相知耳。先生曰。栗谷先生。初与李泼相亲。为共济国事计也。重峰元是泼党。而终至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8H 页
 于绝交也。后曰。侍生亦闻而知之。后曰。李泼之弟溭之外孙李韶甫。方居于李泼之基。先生曰。是何人也。后曰。是石滩李慎仪之孙。而曾以请石滩墓道文字事。进谒先生者也。先生曰。吾亦始记之矣。李慎仪。即昏朝立节之士。故吾亦许其文字而未及构成也。若是李溭外孙。则李溭终不叛牛溪先生。李韶辈亦不变否。后曰。李韶甫尚不变。故使其子云标。参于今夏卞诬之疏章矣。后曰。其侄李云搏。光州高霁峰之外孙而朴判官之妹夫也。但李家皆以松江为雠矣。先生曰。若知李泼母之忌日。则松爷之不杀泼母。分明可知矣。后曰。侍生今年春三月。过李韶甫家问之。则亦以松爷为怨而言曰。己丑祸后庚寅十月。外曾祖母自此移于彼上村。村即李泼村之上也。十二月。被连累而捕致于京。其时赵重峰来要于路傍。赠以毛裘俾御寒。外曾祖母多致慰谢之言。以辛卯五月二十二日。死于压膝之祸云。侍生曰。若然则李家元无归怨于松爷之事。松爷以辛卯二月递相职。仍为远窜于江界。果如李丈之言。则尹氏之死。政在松爷谪在江界之时。而柳成龙委官时尽杀。昭可知矣。李韶甫专信传来之讹言。而不以为然曰。郑相被谪与否
于绝交也。后曰。侍生亦闻而知之。后曰。李泼之弟溭之外孙李韶甫。方居于李泼之基。先生曰。是何人也。后曰。是石滩李慎仪之孙。而曾以请石滩墓道文字事。进谒先生者也。先生曰。吾亦始记之矣。李慎仪。即昏朝立节之士。故吾亦许其文字而未及构成也。若是李溭外孙。则李溭终不叛牛溪先生。李韶辈亦不变否。后曰。李韶甫尚不变。故使其子云标。参于今夏卞诬之疏章矣。后曰。其侄李云搏。光州高霁峰之外孙而朴判官之妹夫也。但李家皆以松江为雠矣。先生曰。若知李泼母之忌日。则松爷之不杀泼母。分明可知矣。后曰。侍生今年春三月。过李韶甫家问之。则亦以松爷为怨而言曰。己丑祸后庚寅十月。外曾祖母自此移于彼上村。村即李泼村之上也。十二月。被连累而捕致于京。其时赵重峰来要于路傍。赠以毛裘俾御寒。外曾祖母多致慰谢之言。以辛卯五月二十二日。死于压膝之祸云。侍生曰。若然则李家元无归怨于松爷之事。松爷以辛卯二月递相职。仍为远窜于江界。果如李丈之言。则尹氏之死。政在松爷谪在江界之时。而柳成龙委官时尽杀。昭可知矣。李韶甫专信传来之讹言。而不以为然曰。郑相被谪与否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8L 页
 及其某年某月。吾不及知。而尹氏之死。果如此云云。侍生闻其言而即记之。以为发明松江搆杀泼母之说矣。先生曰。若果如此则松爷之不杀泼母。不攻自败矣。壬辰乱时。松爷见柳相西崖而责之曰。大监何忍杀泼母与其子也。西崖曰。大监若在则可救乎。松爷曰。吾何忍不救哉。其时答问既如此。泼母之死。又在辛卯五月。则柳相之杀泼母无疑矣。尹氏既有子孙而行忌祀。则以忌日推之。岂不分明乎。后曰。松爷事实如此。而怨归于松爷矣。侍生外高祖李察访某。亦死沈守庆为委官时。而其子孙归怨于松爷。甚可异也。后又作而言曰。先生见佔𠌫斋文集乎。先生曰。未尝得览矣。文集板本在于何处。后曰。未知板本之所在。而借得于人而见之。则其集中甚有可疑之文。所谓万卷堂。即高丽忠肃王往在元朝时。聚得万卷书。作堂而置之。号曰万卷堂。其文所录中。初以李益斋诸人。亦皆同坐陪侍云。而佔𠌫公乃 成庙朝人也。何可厕乎其中。而以余亦厕乎其中书之。又于末端。以翰林学士承旨某记云云。此官名未知果国初所有耶。先生曰。吾不知国初有此官名。忠肃王在高丽之末。佔𠌫斋何可厕于其中耶。必是误录于集也。
及其某年某月。吾不及知。而尹氏之死。果如此云云。侍生闻其言而即记之。以为发明松江搆杀泼母之说矣。先生曰。若果如此则松爷之不杀泼母。不攻自败矣。壬辰乱时。松爷见柳相西崖而责之曰。大监何忍杀泼母与其子也。西崖曰。大监若在则可救乎。松爷曰。吾何忍不救哉。其时答问既如此。泼母之死。又在辛卯五月。则柳相之杀泼母无疑矣。尹氏既有子孙而行忌祀。则以忌日推之。岂不分明乎。后曰。松爷事实如此。而怨归于松爷矣。侍生外高祖李察访某。亦死沈守庆为委官时。而其子孙归怨于松爷。甚可异也。后又作而言曰。先生见佔𠌫斋文集乎。先生曰。未尝得览矣。文集板本在于何处。后曰。未知板本之所在。而借得于人而见之。则其集中甚有可疑之文。所谓万卷堂。即高丽忠肃王往在元朝时。聚得万卷书。作堂而置之。号曰万卷堂。其文所录中。初以李益斋诸人。亦皆同坐陪侍云。而佔𠌫公乃 成庙朝人也。何可厕乎其中。而以余亦厕乎其中书之。又于末端。以翰林学士承旨某记云云。此官名未知果国初所有耶。先生曰。吾不知国初有此官名。忠肃王在高丽之末。佔𠌫斋何可厕于其中耶。必是误录于集也。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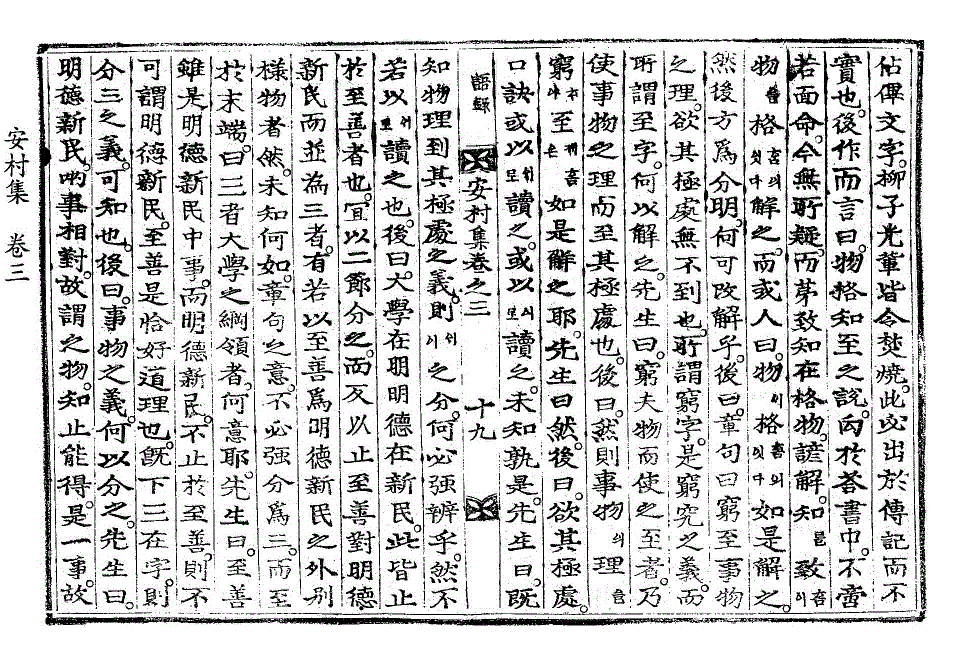 佔𠌫文字。柳子光辈皆令焚烧。此必出于传记而不实也。后作而言曰。物格知至之说。向于答书中。不啻若面命。今无所疑。而第致知在格物。谚解。知()致(홈이)物(을)格(의잇다)解之。而或人曰。物(이)格(홈의잇다)如是解之。然后方为分明。何可改解乎。后曰。章句曰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穷字。是穷究之义。而所谓至字。何以解之。先生曰。穷夫物而使之至者。乃使事物之理而至其极处也。后曰。然则事物(의)理(을)穷(야)至(케홈은)如是解之耶。先生曰然。后曰。欲其极处。口诀或以(로)读之。或以(이로)读之。未知孰是。先生曰。既知物理到其极处之义。则(이)之分。何必强辨乎。然不若以(로)读之也。后曰。大学在明明德在新民。此皆止于至善者也。宜以二节分之。而反以止至善对明德,新民而并为三者。有若以至善为明德新民之外别样物者然。未知何如。章句之意。不必强分为三。而至于末端。曰三者大学之纲领者。何意耶。先生曰。至善虽是明德新民中事。而明德新民。不止于至善。则不可谓明德新民。至善是恰好道理也。既下三在字。则分三之义。可知也。后曰。事物之义。何以分之。先生曰。明德新民。两事相对。故谓之物。知止能得。是一事。故
佔𠌫文字。柳子光辈皆令焚烧。此必出于传记而不实也。后作而言曰。物格知至之说。向于答书中。不啻若面命。今无所疑。而第致知在格物。谚解。知()致(홈이)物(을)格(의잇다)解之。而或人曰。物(이)格(홈의잇다)如是解之。然后方为分明。何可改解乎。后曰。章句曰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穷字。是穷究之义。而所谓至字。何以解之。先生曰。穷夫物而使之至者。乃使事物之理而至其极处也。后曰。然则事物(의)理(을)穷(야)至(케홈은)如是解之耶。先生曰然。后曰。欲其极处。口诀或以(로)读之。或以(이로)读之。未知孰是。先生曰。既知物理到其极处之义。则(이)之分。何必强辨乎。然不若以(로)读之也。后曰。大学在明明德在新民。此皆止于至善者也。宜以二节分之。而反以止至善对明德,新民而并为三者。有若以至善为明德新民之外别样物者然。未知何如。章句之意。不必强分为三。而至于末端。曰三者大学之纲领者。何意耶。先生曰。至善虽是明德新民中事。而明德新民。不止于至善。则不可谓明德新民。至善是恰好道理也。既下三在字。则分三之义。可知也。后曰。事物之义。何以分之。先生曰。明德新民。两事相对。故谓之物。知止能得。是一事。故安村集卷之三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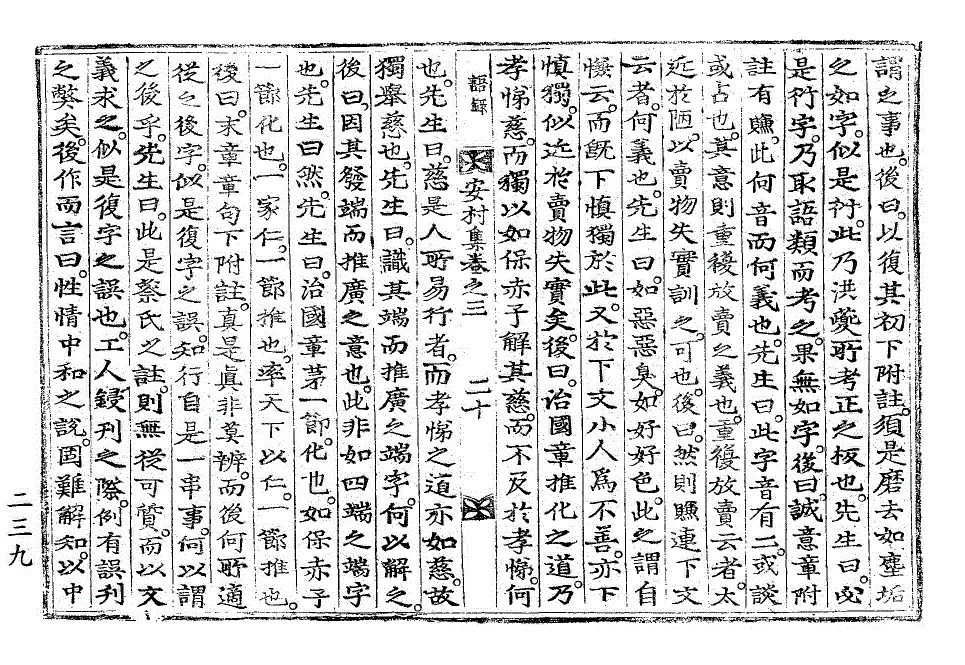 谓之事也。后曰。以复其初下附注。须是磨去如尘垢之如字。似是衍。此乃洪夔所考正之板也。先生曰。必是衍字。乃取语类而考之。果无如字。后曰。诚意章附注有赚。此何音而何义也。先生曰。此字音有二。或谈或占也。其意则重复放卖之义也。重复放卖云者。太近于陋。以卖物失实训之。可也。后曰。然则赚连下文云者。何义也。先生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云。而既下慎独于此。又于下文小人为不善。亦下慎独。似近于卖物失实矣。后曰。治国章推化之道。乃孝悌慈。而独以如保赤子解其慈。而不及于孝悌。何也。先生曰。慈是人所易行者。而孝悌之道亦如慈。故独举慈也。先生曰。识其端而推广之端字。何以解之。后曰。因其发端而推广之意也。此非如四端之端字也。先生曰然。先生曰。治国章第一节。化也。如保赤子一节化也。一家仁。一节推也。率天下以仁。一节推也。后曰。末章章句下附注。真是真非莫辨。而后何所适从之后字。似是复字之误。知行自是一串事。何以谓之后乎。先生曰。此是蔡氏之注。则无从可质。而以文义求之。似是复字之误也。工人锓刊之际。例有误刊之弊矣。后作而言曰。性情中和之说。固难解知。以中
谓之事也。后曰。以复其初下附注。须是磨去如尘垢之如字。似是衍。此乃洪夔所考正之板也。先生曰。必是衍字。乃取语类而考之。果无如字。后曰。诚意章附注有赚。此何音而何义也。先生曰。此字音有二。或谈或占也。其意则重复放卖之义也。重复放卖云者。太近于陋。以卖物失实训之。可也。后曰。然则赚连下文云者。何义也。先生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云。而既下慎独于此。又于下文小人为不善。亦下慎独。似近于卖物失实矣。后曰。治国章推化之道。乃孝悌慈。而独以如保赤子解其慈。而不及于孝悌。何也。先生曰。慈是人所易行者。而孝悌之道亦如慈。故独举慈也。先生曰。识其端而推广之端字。何以解之。后曰。因其发端而推广之意也。此非如四端之端字也。先生曰然。先生曰。治国章第一节。化也。如保赤子一节化也。一家仁。一节推也。率天下以仁。一节推也。后曰。末章章句下附注。真是真非莫辨。而后何所适从之后字。似是复字之误。知行自是一串事。何以谓之后乎。先生曰。此是蔡氏之注。则无从可质。而以文义求之。似是复字之误也。工人锓刊之际。例有误刊之弊矣。后作而言曰。性情中和之说。固难解知。以中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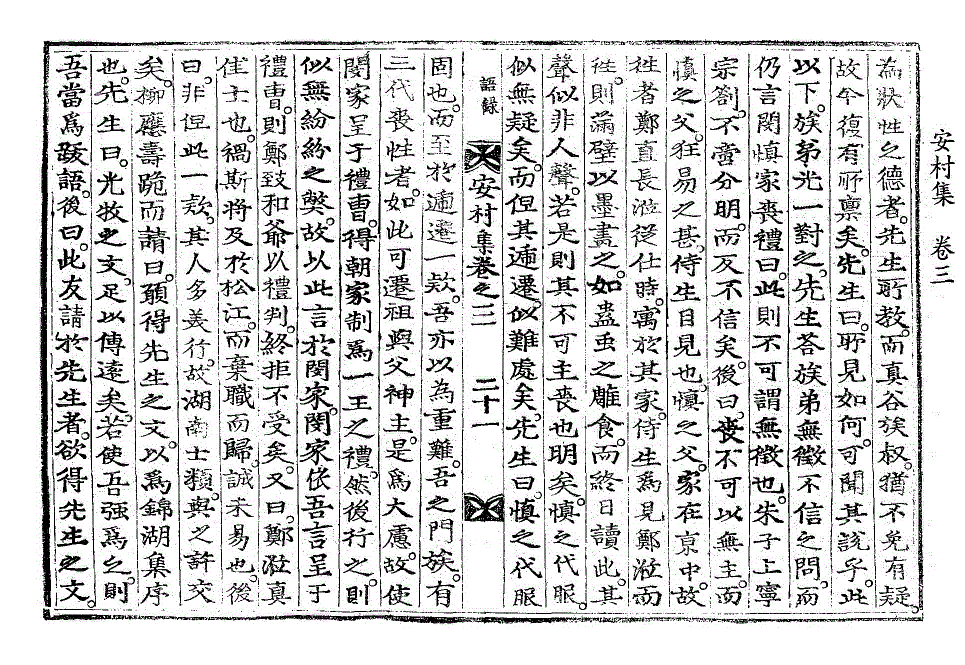 为状性之德者。先生所教。而真谷族叔。犹不免有疑。故今复有所禀矣。先生曰。所见如何。可闻其说乎。此以下。族弟光一对之。先生答族弟无徵不信之问。而仍言闵慎家丧礼曰。此则不可谓无徵也。朱子上宁宗劄。不啻分明。而反不信矣。后曰。丧不可以无主。而慎之父。狂易之甚。侍生目见也。慎之父。家在京中。故往者郑直长涖从仕时。寓于其家。侍生为见郑涖而往。则满壁以墨画之。如蛊虫之雕食。而终日读此。其声似非人声。若是则其不可主丧也明矣。慎之代服。似无疑矣。而但其递迁。似难处矣。先生曰。慎之代服固也。而至于递迁一款。吾亦以为重难。吾之门族。有三代丧性者。如此可迁祖与父神主。是为大虑。故使闵家呈于礼曹。得朝家制为一王之礼。然后行之。则似无纷纷之㢢。故以此言于闵家。闵家依吾言呈于礼曹。则郑致和爷以礼判。终拒不受矣。又曰。郑涖真佳士也。祸斯将及于松江。而弃职而归。诚未易也。后曰。非但此一款。其人多美行。故湖南士类。与之许交矣。柳应寿跪而请曰。愿得先生之文。以为锦湖集序也。先生曰。光牧之文。足以传远矣。若使吾强为之。则吾当为跋语。后曰。此友请于先生者。欲得先生之文。
为状性之德者。先生所教。而真谷族叔。犹不免有疑。故今复有所禀矣。先生曰。所见如何。可闻其说乎。此以下。族弟光一对之。先生答族弟无徵不信之问。而仍言闵慎家丧礼曰。此则不可谓无徵也。朱子上宁宗劄。不啻分明。而反不信矣。后曰。丧不可以无主。而慎之父。狂易之甚。侍生目见也。慎之父。家在京中。故往者郑直长涖从仕时。寓于其家。侍生为见郑涖而往。则满壁以墨画之。如蛊虫之雕食。而终日读此。其声似非人声。若是则其不可主丧也明矣。慎之代服。似无疑矣。而但其递迁。似难处矣。先生曰。慎之代服固也。而至于递迁一款。吾亦以为重难。吾之门族。有三代丧性者。如此可迁祖与父神主。是为大虑。故使闵家呈于礼曹。得朝家制为一王之礼。然后行之。则似无纷纷之㢢。故以此言于闵家。闵家依吾言呈于礼曹。则郑致和爷以礼判。终拒不受矣。又曰。郑涖真佳士也。祸斯将及于松江。而弃职而归。诚未易也。后曰。非但此一款。其人多美行。故湖南士类。与之许交矣。柳应寿跪而请曰。愿得先生之文。以为锦湖集序也。先生曰。光牧之文。足以传远矣。若使吾强为之。则吾当为跋语。后曰。此友请于先生者。欲得先生之文。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0L 页
 以为弁卷之计也。看他文集中。序文不止一二。况朱子既制陈俊卿之状于危祸中。则先生何可固辞乎。先生曰。朱子于危祸中。为跋文则多矣。后乃以族谱所写空册进之。柳应寿亦袖出锦湖集所书空册以进。先生皆亲受。而使畴锡各表记以置之。日已暮矣。拜辞而退。十三日。促饭入先生所问候。先生于昨日。终日酬应。气不安节矣。后曰。光州旧有司马斋。废弃于城中久矣。今城主使之移建于乡校之旁。斯斋适成。城主以文会斋名之。欲得先生之笔揭诸额矣。先生披览光后所编谱牒而教曰。宋判书麒寿。明是蔡忱之婿。而今录于蔡忱妹夫行。必是误书矣。仍以退溪先生所制宋世忠墓碑文示之。世忠。麒寿之父也。果为误书。即改之。后问曰。退溪作此墓道文字。在麒寿为小人之前乎。先生曰。既封麒寿为德恩君。则在乙巳之后矣。后曰。然则退溪何以制之也。先生曰。退溪以应教。亦参于请杀凤城君之劄。故不为深罪乙巳小人矣。其时李晦斋为委官。而杖杀诸贤类。终至于录其勋。郭询不忍其杖。乃呼于庭中曰。岂料吾辈死于复古之手乎。(复古即晦斋字)其后栗谷先生为都宪。郑仁弘为掌令。仁弘欲驳沈青阳义谦。栗谷欲不从。则
以为弁卷之计也。看他文集中。序文不止一二。况朱子既制陈俊卿之状于危祸中。则先生何可固辞乎。先生曰。朱子于危祸中。为跋文则多矣。后乃以族谱所写空册进之。柳应寿亦袖出锦湖集所书空册以进。先生皆亲受。而使畴锡各表记以置之。日已暮矣。拜辞而退。十三日。促饭入先生所问候。先生于昨日。终日酬应。气不安节矣。后曰。光州旧有司马斋。废弃于城中久矣。今城主使之移建于乡校之旁。斯斋适成。城主以文会斋名之。欲得先生之笔揭诸额矣。先生披览光后所编谱牒而教曰。宋判书麒寿。明是蔡忱之婿。而今录于蔡忱妹夫行。必是误书矣。仍以退溪先生所制宋世忠墓碑文示之。世忠。麒寿之父也。果为误书。即改之。后问曰。退溪作此墓道文字。在麒寿为小人之前乎。先生曰。既封麒寿为德恩君。则在乙巳之后矣。后曰。然则退溪何以制之也。先生曰。退溪以应教。亦参于请杀凤城君之劄。故不为深罪乙巳小人矣。其时李晦斋为委官。而杖杀诸贤类。终至于录其勋。郭询不忍其杖。乃呼于庭中曰。岂料吾辈死于复古之手乎。(复古即晦斋字)其后栗谷先生为都宪。郑仁弘为掌令。仁弘欲驳沈青阳义谦。栗谷欲不从。则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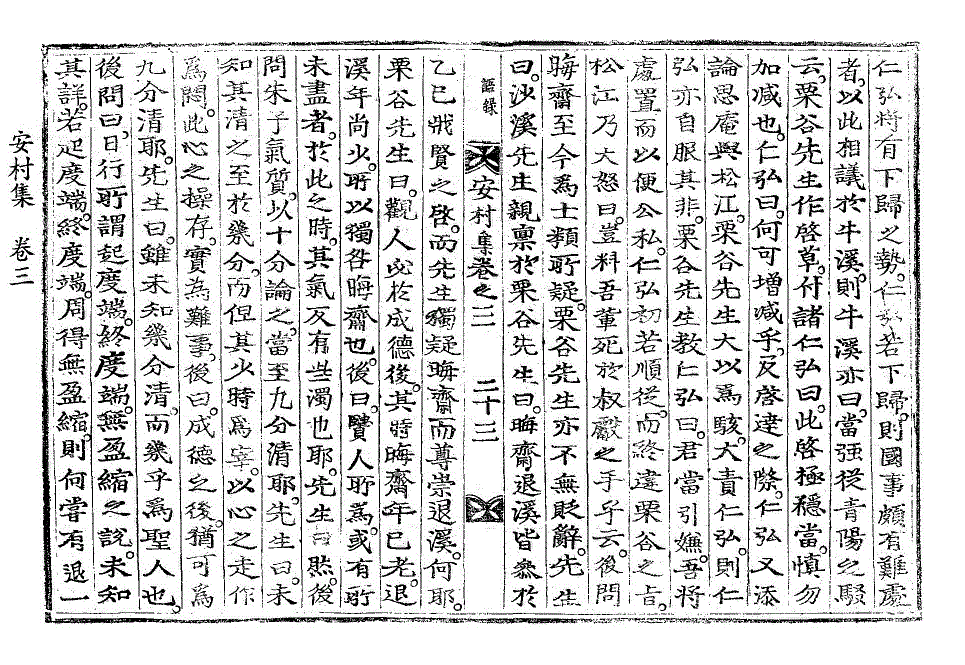 仁弘将有下归之势。仁弘若下归。则国事颇有难处者。以此相议于牛溪。则牛溪亦曰。当强从青阳之驳云。栗谷先生作启草。付诸仁弘曰。此启极稳当。慎勿加减也。仁弘曰。何可增减乎。及启达之际。仁弘又添论思庵与松江。栗谷先生大以为骇。大责仁弘。则仁弘亦自服其非。栗各先生教仁弘曰。君当引嫌。吾将处置而以便公私。仁弘初若顺从。而终违栗谷之旨。松江乃大怒曰。岂料吾辈死于叔献之手乎云。后问晦斋至今为士类所疑。栗谷先生亦不无贬辞。先生曰。沙溪先生亲禀于栗谷先生曰。晦斋,退溪皆参于乙巳戕贤之启。而先生独疑晦斋而尊崇退溪。何耶。栗谷先生曰。观人必于成德后。其时晦斋年已老。退溪年尚少。所以独咎晦斋也。后曰。贤人所为。或有所未尽者。于此之时。其气反有些浊也耶。先生曰然。后问朱子气质。以十分论之。当至九分清耶。先生曰。未知其清之至于几分。而但其少时为宰。以心之走作为闷。此心之操存。实为难事。后曰。成德之后。犹可为九分清耶。先生曰。虽未知几分清。而几乎为圣人也。后问曰。日行所谓起度端。终度端。无盈缩之说。未知其详。若起度端。终度端。周得无盈缩。则何尝有退一
仁弘将有下归之势。仁弘若下归。则国事颇有难处者。以此相议于牛溪。则牛溪亦曰。当强从青阳之驳云。栗谷先生作启草。付诸仁弘曰。此启极稳当。慎勿加减也。仁弘曰。何可增减乎。及启达之际。仁弘又添论思庵与松江。栗谷先生大以为骇。大责仁弘。则仁弘亦自服其非。栗各先生教仁弘曰。君当引嫌。吾将处置而以便公私。仁弘初若顺从。而终违栗谷之旨。松江乃大怒曰。岂料吾辈死于叔献之手乎云。后问晦斋至今为士类所疑。栗谷先生亦不无贬辞。先生曰。沙溪先生亲禀于栗谷先生曰。晦斋,退溪皆参于乙巳戕贤之启。而先生独疑晦斋而尊崇退溪。何耶。栗谷先生曰。观人必于成德后。其时晦斋年已老。退溪年尚少。所以独咎晦斋也。后曰。贤人所为。或有所未尽者。于此之时。其气反有些浊也耶。先生曰然。后问朱子气质。以十分论之。当至九分清耶。先生曰。未知其清之至于几分。而但其少时为宰。以心之走作为闷。此心之操存。实为难事。后曰。成德之后。犹可为九分清耶。先生曰。虽未知几分清。而几乎为圣人也。后问曰。日行所谓起度端。终度端。无盈缩之说。未知其详。若起度端。终度端。周得无盈缩。则何尝有退一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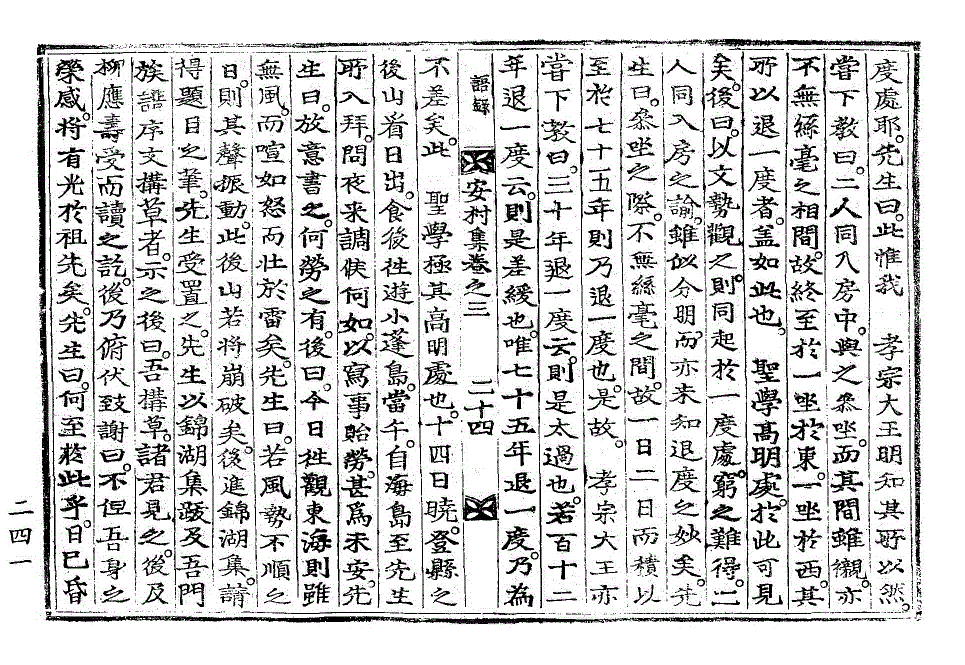 度处耶。先生曰。此惟我 孝宗大王明知其所以然。尝下教曰。二人同入房中。与之参坐。而其间虽衬。亦不无丝毫之相间。故终至于一坐于东。一坐于西。其所以退一度者。盖如此也。 圣学高明处。于此可见矣。后曰。以文势观之。则同起于一度处。穷之难得。二人同入房之谕。虽似分明。而亦未知退度之妙矣。先生曰。参坐之际。不无丝毫之间。故一日二日而积以至于七十五年则乃退一度也。是故。 孝宗大王亦尝下教曰。三十年退一度云。则是太过也。若百十二年退一度云。则是差缓也。唯七十五年退一度。乃为不差矣。此 圣学极其高明处也。十四日晓。登县之后山看日出。食后往游小蓬岛。当午。自海岛至先生所入拜。问夜来调候何如。以写事贻劳。甚为未安。先生曰。放意书之。何劳之有。后曰。今日往观东海则虽无风。而喧如怒而壮于雷矣。先生曰。若风势不顺之日。则其声振动。此后山若将崩破矣。后进锦湖集。请得题目之笔。先生受置之。先生以锦湖集跋及吾门族谱序文搆草者。示之后曰。吾搆草。诸君见之。后及柳应寿受而读之讫。后乃俯伏致谢曰。不但吾身之荣感。将有光于祖先矣。先生曰。何至于此乎。日已昏
度处耶。先生曰。此惟我 孝宗大王明知其所以然。尝下教曰。二人同入房中。与之参坐。而其间虽衬。亦不无丝毫之相间。故终至于一坐于东。一坐于西。其所以退一度者。盖如此也。 圣学高明处。于此可见矣。后曰。以文势观之。则同起于一度处。穷之难得。二人同入房之谕。虽似分明。而亦未知退度之妙矣。先生曰。参坐之际。不无丝毫之间。故一日二日而积以至于七十五年则乃退一度也。是故。 孝宗大王亦尝下教曰。三十年退一度云。则是太过也。若百十二年退一度云。则是差缓也。唯七十五年退一度。乃为不差矣。此 圣学极其高明处也。十四日晓。登县之后山看日出。食后往游小蓬岛。当午。自海岛至先生所入拜。问夜来调候何如。以写事贻劳。甚为未安。先生曰。放意书之。何劳之有。后曰。今日往观东海则虽无风。而喧如怒而壮于雷矣。先生曰。若风势不顺之日。则其声振动。此后山若将崩破矣。后进锦湖集。请得题目之笔。先生受置之。先生以锦湖集跋及吾门族谱序文搆草者。示之后曰。吾搆草。诸君见之。后及柳应寿受而读之讫。后乃俯伏致谢曰。不但吾身之荣感。将有光于祖先矣。先生曰。何至于此乎。日已昏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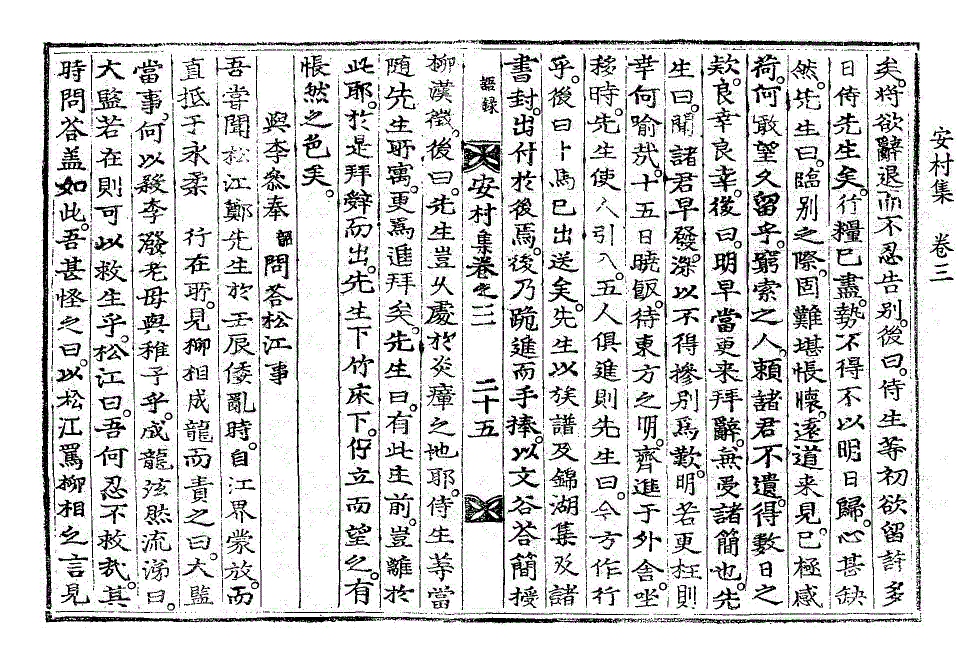 矣。将欲辞退而不忍告别。后曰。侍生等初欲留许多日侍先生矣。行粮已尽。势不得不以明日归。心甚缺然。先生曰。临别之际。固难堪怅怀。远道来见。已极感荷。何敢望久留乎。穷索之人。赖诸君不遗。得数日之款。良幸良幸。后曰。明早当更来拜辞。兼受诸简也。先生曰。闻诸君早发。深以不得掺别为叹。明若更枉则幸何喻哉。十五日晓饭。待东方之明。齐进于外舍。坐移时。先生使人引入。五人俱进则先生曰。今方作行乎。后曰卜马已出送矣。先生以族谱及锦湖集及诸书封。出付于后焉。后乃跪进而手捧。以文谷答简授柳汉徵。后曰。先生岂久处于炎瘴之地耶。侍生等当随先生所寓。更为进拜矣。先生曰。有此生前。岂离于此耶。于是拜辞而出。先生下竹床下。伫立而望之。有怅然之色矣。
矣。将欲辞退而不忍告别。后曰。侍生等初欲留许多日侍先生矣。行粮已尽。势不得不以明日归。心甚缺然。先生曰。临别之际。固难堪怅怀。远道来见。已极感荷。何敢望久留乎。穷索之人。赖诸君不遗。得数日之款。良幸良幸。后曰。明早当更来拜辞。兼受诸简也。先生曰。闻诸君早发。深以不得掺别为叹。明若更枉则幸何喻哉。十五日晓饭。待东方之明。齐进于外舍。坐移时。先生使人引入。五人俱进则先生曰。今方作行乎。后曰卜马已出送矣。先生以族谱及锦湖集及诸书封。出付于后焉。后乃跪进而手捧。以文谷答简授柳汉徵。后曰。先生岂久处于炎瘴之地耶。侍生等当随先生所寓。更为进拜矣。先生曰。有此生前。岂离于此耶。于是拜辞而出。先生下竹床下。伫立而望之。有怅然之色矣。与李参奉(韶)问答松江事
吾尝闻松江郑先生于壬辰倭乱时。自江界蒙放。而直抵于永柔 行在所。见柳相成龙而责之曰。大监当事。何以杀李泼老母与稚子乎。成龙泫然流涕曰。大监若在则可以救生乎。松江曰。吾何忍不救哉。其时问答盖如此。吾甚怪之曰。以松江骂柳相之言见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2L 页
 之。则泼母与泼子之死。似若在松江被谪之后。而一边之人。必以是事归之松江。而至今为祸阶者何耶。若使松爷在朝之日。果杀泼母与𥠧子。则虽非松爷为委官之时。而松江与成龙。同在相席。岂无相见面话之日。而必待永柔乱离中相责耶。以是为疑于心者久矣。岁丁巳春三月。适以事往南平。与洪润河拜李丈韶。韶即李泼弟进士李溭之外孙也。其人颇纯实。可以询往事。且守李家之基业而至今居生。故吾以己丑事详问之。则李丈嘘噫有不平色。乃整容而对曰。己丑之祸。言之惨矣。李承旨兄弟就戮之后。外曾祖母尹氏。以庚寅十月移寓于彼上村。(上村即李泼所居之村也)十二月。又被连累。捕致于京。赵重峰于路中。迎拜尹氏。以毛裘一袭俾御其寒。尹氏多致慰谢之言。仍囚系于王狱者屡月。外祖母亦随往而救其狱。以辛卯五月二十二日。外曾祖母死于压膝之祸云。吾疑其李丈之言有舛误。复问曰。己丑之狱。果若是留滞耶。李丈曰。李承旨之兄李井邑汲之子。自祸后久囚于狱。始得蒙放于壬辰之乱。其屡年蔓祸。此可知矣。吾乃作而言曰。然则尹氏之死。在松江见谪之后矣。今之人。何以尹氏之死归怨于松爷耶。李丈曰。吾侍
之。则泼母与泼子之死。似若在松江被谪之后。而一边之人。必以是事归之松江。而至今为祸阶者何耶。若使松爷在朝之日。果杀泼母与𥠧子。则虽非松爷为委官之时。而松江与成龙。同在相席。岂无相见面话之日。而必待永柔乱离中相责耶。以是为疑于心者久矣。岁丁巳春三月。适以事往南平。与洪润河拜李丈韶。韶即李泼弟进士李溭之外孙也。其人颇纯实。可以询往事。且守李家之基业而至今居生。故吾以己丑事详问之。则李丈嘘噫有不平色。乃整容而对曰。己丑之祸。言之惨矣。李承旨兄弟就戮之后。外曾祖母尹氏。以庚寅十月移寓于彼上村。(上村即李泼所居之村也)十二月。又被连累。捕致于京。赵重峰于路中。迎拜尹氏。以毛裘一袭俾御其寒。尹氏多致慰谢之言。仍囚系于王狱者屡月。外祖母亦随往而救其狱。以辛卯五月二十二日。外曾祖母死于压膝之祸云。吾疑其李丈之言有舛误。复问曰。己丑之狱。果若是留滞耶。李丈曰。李承旨之兄李井邑汲之子。自祸后久囚于狱。始得蒙放于壬辰之乱。其屡年蔓祸。此可知矣。吾乃作而言曰。然则尹氏之死。在松江见谪之后矣。今之人。何以尹氏之死归怨于松爷耶。李丈曰。吾侍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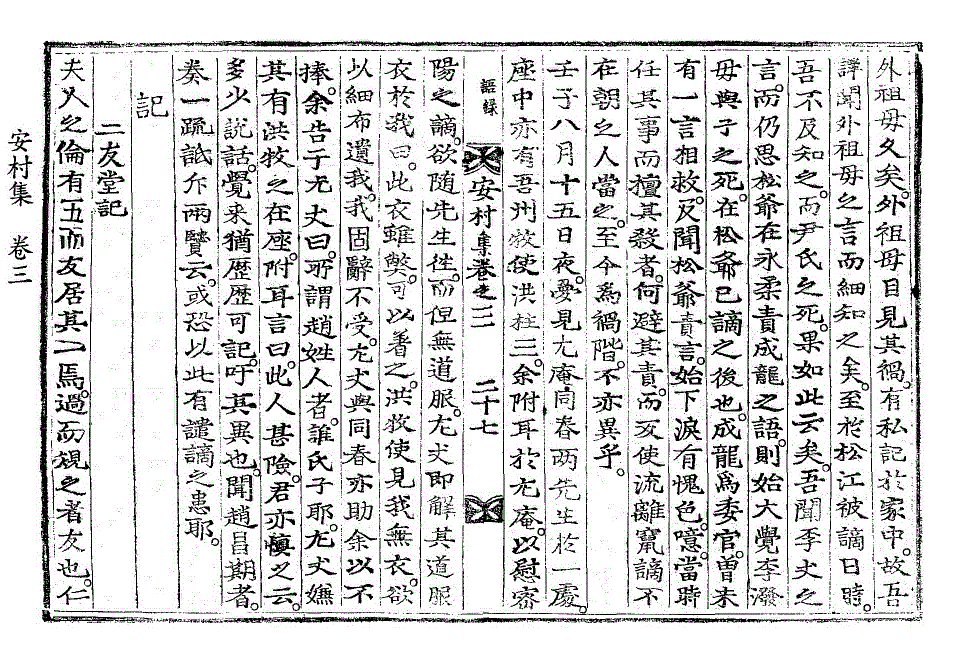 外祖母久矣。外祖母目见其祸。有私记于家中。故吾详闻外祖母之言而细知之矣。至于松江被谪日时。吾不及知之。而尹氏之死。果如此云矣。吾闻李丈之言。而仍思松爷在永柔责成龙之语。则始大觉李泼母与子之死。在松爷已谪之后也。成龙为委官。曾未有一言相救。及闻松爷责言。始下泪有愧色。噫。当时任其事而擅其杀者。何避其责。而反使流离窜谪不在朝之人当之。至今为祸阶。不亦异乎。
外祖母久矣。外祖母目见其祸。有私记于家中。故吾详闻外祖母之言而细知之矣。至于松江被谪日时。吾不及知之。而尹氏之死。果如此云矣。吾闻李丈之言。而仍思松爷在永柔责成龙之语。则始大觉李泼母与子之死。在松爷已谪之后也。成龙为委官。曾未有一言相救。及闻松爷责言。始下泪有愧色。噫。当时任其事而擅其杀者。何避其责。而反使流离窜谪不在朝之人当之。至今为祸阶。不亦异乎。壬子八月十五日夜。梦见尤庵,同春两先生于一处。座中亦有吾州牧使洪柱三。余附耳于尤庵。以慰密阳之谪。欲随先生往。而但无道服。尤丈即解其道服衣于我曰。此衣虽㢢。可以着之。洪牧使见我无衣。欲以细布遗我。我固辞不受。尤丈与同春亦助余以不捧。余告于尤丈曰。所谓赵姓人者。谁氏子耶。尤丈嫌其有洪牧之在座。附耳言曰。此人甚险。君亦慎之云。多少说话。觉来犹历历可记。吁其异也。闻赵昌期者。奏一疏诋斥两贤云。或恐以此有谴谪之患耶。
安村集卷之三
记
二友堂记
夫人之伦有五而友居其一焉。过而规之者友也。仁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3L 页
 而辅之者友也。自古圣人贤士。莫不以友为重且大焉。其曰友直,友谅,友多闻者。岂不以资友之直而谅而多闻。而为己之直也谅也多闻也乎。然则人有是仁而吾取而为法者。友之道也。吾有是过而人随而为正者。友之道也。其相须之益。可谓殷矣。今之所谓友者。亦有如古之所谓友者乎。诩诩谈笑。未免俳谐而已。区区便佞。只为势利而已。若是而曰吾有友焉。则人孰不窃笑之乎。是以有志之士常慨然于斯。友于今而不得于今。则必尚友于古而曰嘐嘐然。友于人而不得其人。则必寓兴于物而曰嚣嚣然。此岂人之必欲舍今而取古。外人而求物哉。吾以是道求友于今。而今无以是道友于吾者。乃夷考古之人而得其人焉。周公之多艺也。孔子之雅言也。以至颜,曾,思,孟之慎思明辨。开卷瞭然。肝胆自照则周,张,程,朱之继往开来。莫不昭垂于方册。而吾之取以为友者在此焉。吾以是意取友于人。而人无以是意友于吾者。乃援引物之类而得其物焉。老竹千挺。森立于前。风来有韵。警我之心。雪压不屈。励我之节。直插云霄。有壁立千仞之像。寒侵几案。无查滓一点之累。而可以吟于斯咏于斯。则吾之取以为友者在此焉。左右图
而辅之者友也。自古圣人贤士。莫不以友为重且大焉。其曰友直,友谅,友多闻者。岂不以资友之直而谅而多闻。而为己之直也谅也多闻也乎。然则人有是仁而吾取而为法者。友之道也。吾有是过而人随而为正者。友之道也。其相须之益。可谓殷矣。今之所谓友者。亦有如古之所谓友者乎。诩诩谈笑。未免俳谐而已。区区便佞。只为势利而已。若是而曰吾有友焉。则人孰不窃笑之乎。是以有志之士常慨然于斯。友于今而不得于今。则必尚友于古而曰嘐嘐然。友于人而不得其人。则必寓兴于物而曰嚣嚣然。此岂人之必欲舍今而取古。外人而求物哉。吾以是道求友于今。而今无以是道友于吾者。乃夷考古之人而得其人焉。周公之多艺也。孔子之雅言也。以至颜,曾,思,孟之慎思明辨。开卷瞭然。肝胆自照则周,张,程,朱之继往开来。莫不昭垂于方册。而吾之取以为友者在此焉。吾以是意取友于人。而人无以是意友于吾者。乃援引物之类而得其物焉。老竹千挺。森立于前。风来有韵。警我之心。雪压不屈。励我之节。直插云霄。有壁立千仞之像。寒侵几案。无查滓一点之累。而可以吟于斯咏于斯。则吾之取以为友者在此焉。左右图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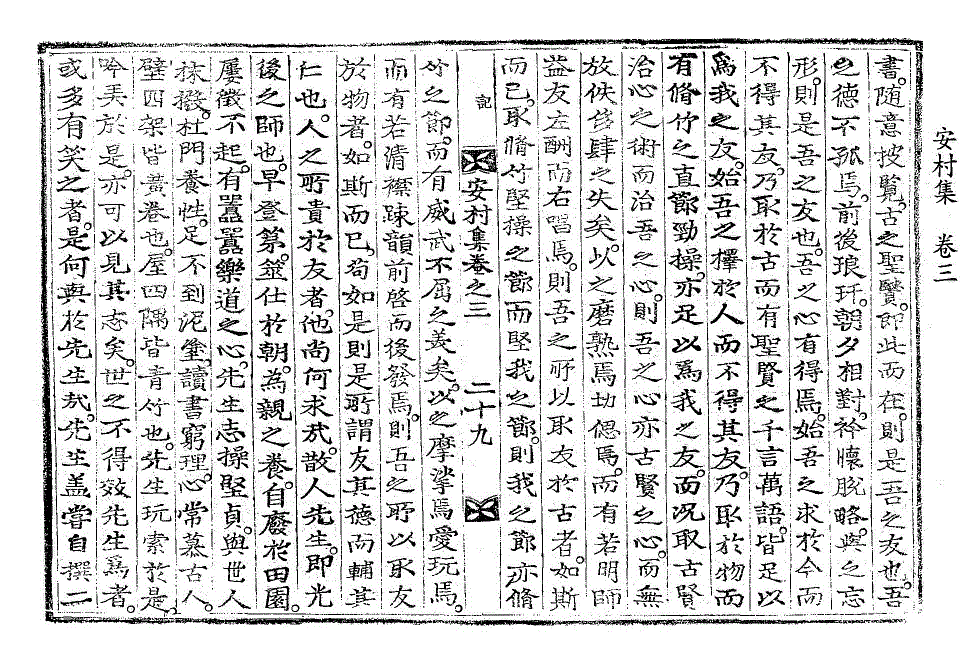 书。随意披览。古之圣贤。即此而在。则是吾之友也。吾之德不孤焉。前后琅玕。朝夕相对。衿怀脱略。与之忘形。则是吾之友也。吾之心有得焉。始吾之求于今而不得其友。乃取于古而有圣贤之千言万语。皆足以为我之友。始吾之择于人而不得其友。乃取于物而有脩竹之直节劲操。亦足以为我之友。而况取古贤治心之术而治吾之心。则吾之心亦古贤之心。而无放佚侈肆之失矣。以之磨熟焉切偲焉。而有若明师益友左酬而右唱焉。则吾之所以取友于古者。如斯而已。取脩竹坚操之节而坚我之节。则我之节亦脩竹之节。而有威武不屈之美矣。以之摩挲焉爱玩焉。而有若清襟疏韵前启而后发焉。则吾之所以取友于物者。如斯而已。苟如是则是所谓友其德而辅其仁也。人之所贵于友者。他尚何求哉。散人先生。即光后之师也。早登第。筮仕于朝。为亲之养。自废于田园。屡徵不起。有嚣嚣乐道之心。先生志操坚贞。与世人抹摋。杜门养性。足不到泥涂。读书穷理。心常慕古人。壁四架皆黄卷也。屋四隅皆青竹也。先生玩索于是。吟弄于是。亦可以见其志矣。世之不得效先生为者。或多有笑之者。是何与于先生哉。先生盖尝自撰二
书。随意披览。古之圣贤。即此而在。则是吾之友也。吾之德不孤焉。前后琅玕。朝夕相对。衿怀脱略。与之忘形。则是吾之友也。吾之心有得焉。始吾之求于今而不得其友。乃取于古而有圣贤之千言万语。皆足以为我之友。始吾之择于人而不得其友。乃取于物而有脩竹之直节劲操。亦足以为我之友。而况取古贤治心之术而治吾之心。则吾之心亦古贤之心。而无放佚侈肆之失矣。以之磨熟焉切偲焉。而有若明师益友左酬而右唱焉。则吾之所以取友于古者。如斯而已。取脩竹坚操之节而坚我之节。则我之节亦脩竹之节。而有威武不屈之美矣。以之摩挲焉爱玩焉。而有若清襟疏韵前启而后发焉。则吾之所以取友于物者。如斯而已。苟如是则是所谓友其德而辅其仁也。人之所贵于友者。他尚何求哉。散人先生。即光后之师也。早登第。筮仕于朝。为亲之养。自废于田园。屡徵不起。有嚣嚣乐道之心。先生志操坚贞。与世人抹摋。杜门养性。足不到泥涂。读书穷理。心常慕古人。壁四架皆黄卷也。屋四隅皆青竹也。先生玩索于是。吟弄于是。亦可以见其志矣。世之不得效先生为者。或多有笑之者。是何与于先生哉。先生盖尝自撰二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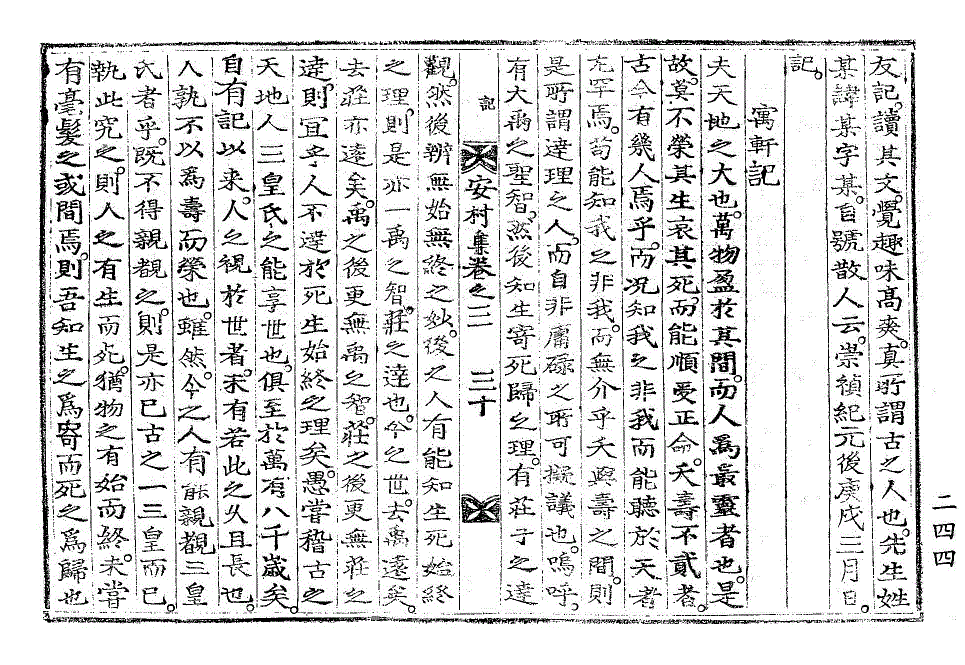 友记。读其文。觉趣味高爽。真所谓古之人也。先生姓某讳某字某。自号散人云。崇祯纪元后庚戌三月日。记。
友记。读其文。觉趣味高爽。真所谓古之人也。先生姓某讳某字某。自号散人云。崇祯纪元后庚戌三月日。记。寓轩记
夫天地之大也。万物盈于其间。而人为最灵者也。是故。莫不荣其生哀其死。而能顺受正命。夭寿不贰者。古今有几人焉乎。而况知我之非我而能听于天者尤罕焉。苟能知我之非我。而无介乎夭与寿之间。则是所谓达理之人。而自非庸碌之所可拟议也。呜呼。有大禹之圣智。然后知生寄死归之理。有庄子之达观。然后辨无始无终之妙。后之人有能知生死始终之理。则是亦一禹之智。庄之达也。今之世。去禹远矣。去庄亦远矣。禹之后更无禹之智。庄之后更无庄之达。则宜乎人不达于死生始终之理矣。愚尝稽古之天地人三皇氏之能享世也。俱至于万有八千岁矣。自有记以来。人之视于世者。未有若此之久且长也。人孰不以为寿而荣也。虽然。今之人有能亲睹三皇氏者乎。既不得亲睹之。则是亦已古之一三皇而已。执此究之。则人之有生而死。犹物之有始而终。未尝有毫发之或间焉。则吾知生之为寄而死之为归也
安村集卷之三 第 245H 页
 明矣。容有所欣戚于一寿一夭之间乎。光后之再从叔尚玄甫。博雅君子也。于死生始终之理。早有契焉。而必勉人曰。人间事莫不有数。荣辱得丧。亦尚有荣辱得丧之数。则死生寿夭。亦岂无死生寿夭之理乎。既有其理。则人可以苟图其生而苟免其死乎。不可以苟图而苟免。则吾之生也寓于形。而吾之死也非归于理乎。此吾所以揭寓名轩者也。光后闻其言而有感于心。反以诫之曰。智哉子之心。其有禹之智乎。达哉子之言。其有庄之达乎。虽然。知生之为寄而孜孜为善。寸阴是惜者禹也。知始之必终而秘迹林泉。颐养精神者庄也。子其效禹之孜孜者乎。效庄之秘迹者乎。择于斯二者而知有以处之。则斯可谓不悖其所生之理。而知寓之为寓矣。子其勉之。族侄为寓翁书。
明矣。容有所欣戚于一寿一夭之间乎。光后之再从叔尚玄甫。博雅君子也。于死生始终之理。早有契焉。而必勉人曰。人间事莫不有数。荣辱得丧。亦尚有荣辱得丧之数。则死生寿夭。亦岂无死生寿夭之理乎。既有其理。则人可以苟图其生而苟免其死乎。不可以苟图而苟免。则吾之生也寓于形。而吾之死也非归于理乎。此吾所以揭寓名轩者也。光后闻其言而有感于心。反以诫之曰。智哉子之心。其有禹之智乎。达哉子之言。其有庄之达乎。虽然。知生之为寄而孜孜为善。寸阴是惜者禹也。知始之必终而秘迹林泉。颐养精神者庄也。子其效禹之孜孜者乎。效庄之秘迹者乎。择于斯二者而知有以处之。则斯可谓不悖其所生之理。而知寓之为寓矣。子其勉之。族侄为寓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