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记
记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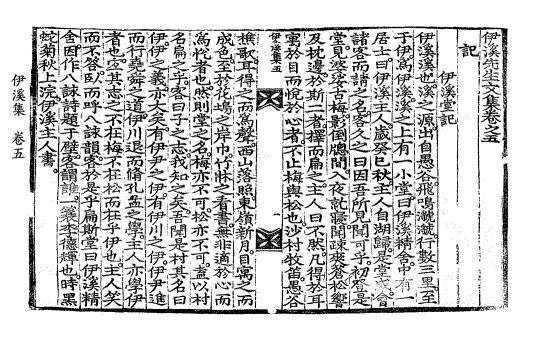 伊溪堂记
伊溪堂记伊溪溪也。溪之源。出自愚谷。飞鸣㶁㶁。行数三里。至于伊。为伊溪。溪之上有一小堂。曰伊溪精舍。中有一居士。曰伊溪主人。岁癸巳秋。主人自湖归。是堂成。会诸客而请之名。客久之曰因吾所见闻可乎。初登是堂。见婆娑古梅。影倒窗间。入夜就寝。闻疏爽苍松响及枕边。于斯二者。择而扁之。主人曰不然。凡得于耳寓于目而悦于心者。不止梅与松也。沙村牧笛。愚谷樵歌。耳得之而为声。西山落照。东岭新月。目寓之而成色。至于花坞之岸巾。竹床之看书。无非适于心而为悦者也。然则堂之名。梅亦不可。松亦不可。盍以村名扁之乎。客曰子之志。我知之矣。吾闻是村其名曰伊。伊之义。亦大矣。有伊尹之伊。有伊川之伊。伊尹进而行尧舜之道。伊川退而脩孔孟之学。主人亦学伊者也。宜其志之不在梅不在松而在乎伊也。主人笑而不答。卧而呼八咏韵。客于是乎扁斯堂曰伊溪精舍。因作八咏诗题于壁。客谓谁。一蓑李德辉也。时黑蛇菊秋上浣。伊溪主人书。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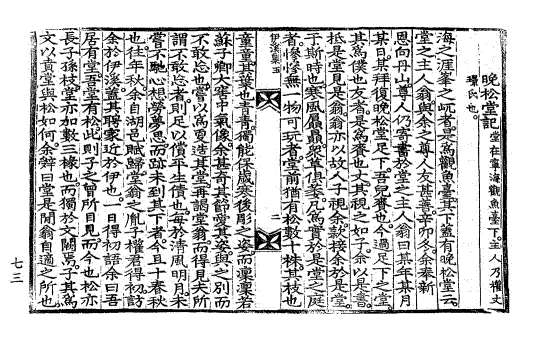 晚松堂记(堂在宁海观鱼台下。主人乃权丈璟氏也。)
晚松堂记(堂在宁海观鱼台下。主人乃权丈璟氏也。)海之涯峰之屼者。是为观鱼台。其下盖有晚松堂云。堂之主人翁。与余之尊人友甚善。辛卯冬。余奉新 恩向丹山。尊人仍寄书于堂之主人翁曰某年某月某日。某拜复晚松堂足下。吾儿赉也。今过足下之堂。其为仆也友者。是为赉也丈。其视之如子。余以是书。抵是堂见是翁。翁亦以故人子视余。款接余于是堂。于斯时也。寒风屃赑。众草俱萎。凡为实于是堂之庭者。惨惨无一物可玩者。堂前犹有松数十株。其枝也童童。其叶也青青。独能保岁寒后彫之姿。而凛凛若苏子卿大窖中气像。余甚奇其节爱其姿。与之别而不敢忘也。尝以为更造其堂。再谒堂翁。而得见夫所谓不敢忘者。则足以偿平生债也。每于清风明月。未尝不驰心想劳梦思。而迹未到其下者。今且十春秋也。往年秋。余自湖邑赋归。堂翁之胤子权君得初。访余于伊溪。盖其聘家近于伊也。一日得初语余曰吾居有堂。吾堂有松。此则子之曾所目见。而今也松亦长子孙枝。堂亦加数三椽也。而独于文阙焉。子其为文以贲堂与松如何。余辞曰堂是閒翁自适之所也。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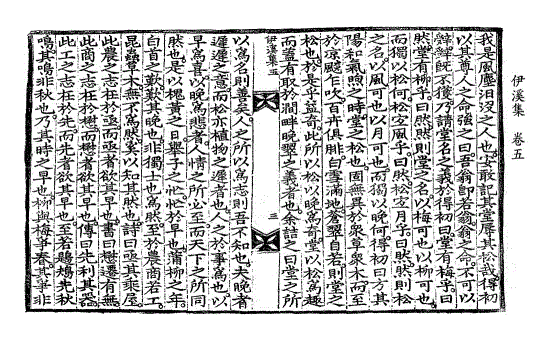 我是风尘汩没之人也。安敢记其堂辱其松哉。得初以其尊人之命强之曰。吾翁即若翁。翁之命。不可以辞。辞既不获。乃请堂名之义于得初曰。堂有梅乎。曰然。堂有柳乎。曰然。然则堂之名。以梅可也以柳可也。而独以松何。松宜风乎。曰然。松宜月乎。曰然。然则松之名。以风可也以月可也。而独以晚何。得初曰方其阳和气煦之时。堂之松也。固无异于众草众木。而至于凉飙乍吹。百卉俱腓。白雪满地。苍翠自若。则堂之松也。于是乎益奇。此所以松以晚为奇。堂以松为趣而盖有取于涧畔晚翠之义者也。余诘之曰堂之所以为名则善矣。人之所以为志则吾不知也。夫晚者迟迟之意。而松亦植物之迟者也。人之于事为也。以早为喜。以晚为悲者。人情之所必至。而天下之所同然也。是以槐黄之日。举子之忙。忙于早也。蒲柳之年。白首之叹。叹其晚也。非独士也为然。至于农商若工。昆虫草木。无不为然。奚以知其然也。诗曰亟其乘屋。此农之志在于亟。而亟者欲其早也。书曰懋迁有无。此商之志在于懋。而懋者欲其早也。传曰先利其器。此工之志在于先。而先者欲其早也。至若鶗鴂先秋鸣。其鸣非秋也。乃其时之早也。柳与梅争春。其争非
我是风尘汩没之人也。安敢记其堂辱其松哉。得初以其尊人之命强之曰。吾翁即若翁。翁之命。不可以辞。辞既不获。乃请堂名之义于得初曰。堂有梅乎。曰然。堂有柳乎。曰然。然则堂之名。以梅可也以柳可也。而独以松何。松宜风乎。曰然。松宜月乎。曰然。然则松之名。以风可也以月可也。而独以晚何。得初曰方其阳和气煦之时。堂之松也。固无异于众草众木。而至于凉飙乍吹。百卉俱腓。白雪满地。苍翠自若。则堂之松也。于是乎益奇。此所以松以晚为奇。堂以松为趣而盖有取于涧畔晚翠之义者也。余诘之曰堂之所以为名则善矣。人之所以为志则吾不知也。夫晚者迟迟之意。而松亦植物之迟者也。人之于事为也。以早为喜。以晚为悲者。人情之所必至。而天下之所同然也。是以槐黄之日。举子之忙。忙于早也。蒲柳之年。白首之叹。叹其晚也。非独士也为然。至于农商若工。昆虫草木。无不为然。奚以知其然也。诗曰亟其乘屋。此农之志在于亟。而亟者欲其早也。书曰懋迁有无。此商之志在于懋。而懋者欲其早也。传曰先利其器。此工之志在于先。而先者欲其早也。至若鶗鴂先秋鸣。其鸣非秋也。乃其时之早也。柳与梅争春。其争非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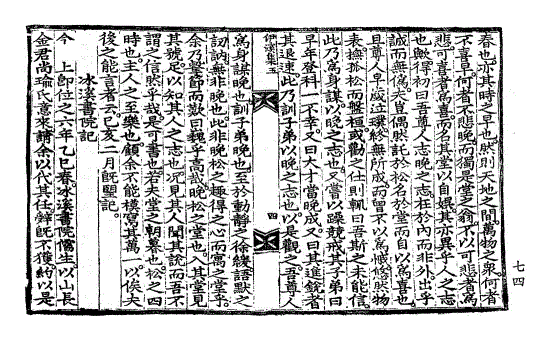 春也。亦其时之早也。然则天地之间。万物之众。何者不喜早。何者不悲晚。而独是堂之翁。不以可悲者为悲。可喜者为喜。而名其堂以自娱。其亦异乎人之志也欤。得初曰吾尊人志晚之志。在于内而非外。出乎诚而无伪。夫岂偶然托于松名于堂而自以为喜也。且尊人早岁泣璞。终无所成。而曾不以为戚。悠然物表。抚孤松而盘桓。或劝之仕则辄曰吾斯之未能信。此乃为身谋。以晚之志也。又尝以躁竞戒其子弟曰早年登科一不幸。又曰大才当晚成。又曰其进锐者其退速。此乃训子弟以晚之志也。以是观之。吾尊人为身谋晚也。训子弟晚也。至于动静之徐缓。语默之讱讷。无非晚也。此非晚松之趣得之心而寓之堂乎。余乃击节而叹曰巍乎高哉。晚松之堂也。入其堂见其号。足以知其人之志也。况见其人闻其说而吾不谓之信然乎哉。是可书也。若夫堂之朝暮也。松之四时也。主人之至乐也。顾余不能模写其万一。以俟夫后之能言者云。己亥二月既望记。
春也。亦其时之早也。然则天地之间。万物之众。何者不喜早。何者不悲晚。而独是堂之翁。不以可悲者为悲。可喜者为喜。而名其堂以自娱。其亦异乎人之志也欤。得初曰吾尊人志晚之志。在于内而非外。出乎诚而无伪。夫岂偶然托于松名于堂而自以为喜也。且尊人早岁泣璞。终无所成。而曾不以为戚。悠然物表。抚孤松而盘桓。或劝之仕则辄曰吾斯之未能信。此乃为身谋。以晚之志也。又尝以躁竞戒其子弟曰早年登科一不幸。又曰大才当晚成。又曰其进锐者其退速。此乃训子弟以晚之志也。以是观之。吾尊人为身谋晚也。训子弟晚也。至于动静之徐缓。语默之讱讷。无非晚也。此非晚松之趣得之心而寓之堂乎。余乃击节而叹曰巍乎高哉。晚松之堂也。入其堂见其号。足以知其人之志也。况见其人闻其说而吾不谓之信然乎哉。是可书也。若夫堂之朝暮也。松之四时也。主人之至乐也。顾余不能模写其万一。以俟夫后之能言者云。己亥二月既望记。冰溪书院记
今 上即位之六年乙巳春。冰溪书院儒生。以山长金君尚瑜氏意来。请余以代其任。辞既不获。约以是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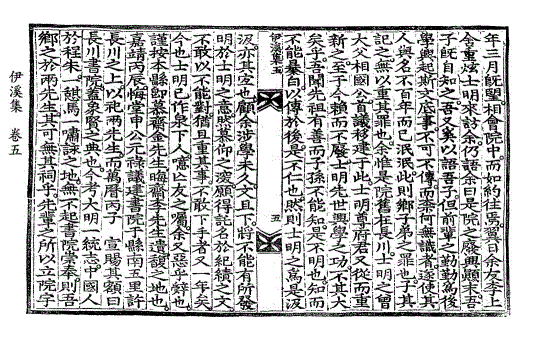 年三月既望。相会院中。而如约往焉。翼日余友李上舍重炫士明来访余。仍语余曰是院之废兴颠末。吾子既自知之。吾又奚以语吾子。但前辈之勤勤为后学兴起斯文底事。不可不传。而柰何无识者。遂使其人与名不百年而已泯泯。此则乡子弟之罪也。子其记之。无以重其罪也。余惟是院旧在长川。士明之曾大父相国公。首议移建于此。士明尊府君又从而重新之。至于今赖而不废。士明先世兴学之功。不其大矣乎。吾闻先祖有善而子孙不能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能㬥白。以传于后。是不仁也。然则士明之为是汲汲。亦其宜也。顾余涉学未久。文且下。将不能有所发明于士明之意。然慕仰之深。愿得托名于纪绩之文。不敢以不能对。犹且重其事。不敢下手者又一年矣。今也士明已作泉下人。噫亡友之嘱。余又恶乎辞也。谨按本县即慕斋金先生,晦斋李先生遗馥之地也。嘉靖丙辰。悔堂申公元禄议建书院于县南五里许长川之上。以祀两先生。而万历丙子 宣赐其额曰长川书院。盖象贤之典也。今考大明一统志。中国人于程朱。一憩马一啸咏之地。无不起书院崇奉。则吾乡之于两先生。其可无其祠乎。先辈之所以立院宇
年三月既望。相会院中。而如约往焉。翼日余友李上舍重炫士明来访余。仍语余曰是院之废兴颠末。吾子既自知之。吾又奚以语吾子。但前辈之勤勤为后学兴起斯文底事。不可不传。而柰何无识者。遂使其人与名不百年而已泯泯。此则乡子弟之罪也。子其记之。无以重其罪也。余惟是院旧在长川。士明之曾大父相国公。首议移建于此。士明尊府君又从而重新之。至于今赖而不废。士明先世兴学之功。不其大矣乎。吾闻先祖有善而子孙不能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能㬥白。以传于后。是不仁也。然则士明之为是汲汲。亦其宜也。顾余涉学未久。文且下。将不能有所发明于士明之意。然慕仰之深。愿得托名于纪绩之文。不敢以不能对。犹且重其事。不敢下手者又一年矣。今也士明已作泉下人。噫亡友之嘱。余又恶乎辞也。谨按本县即慕斋金先生,晦斋李先生遗馥之地也。嘉靖丙辰。悔堂申公元禄议建书院于县南五里许长川之上。以祀两先生。而万历丙子 宣赐其额曰长川书院。盖象贤之典也。今考大明一统志。中国人于程朱。一憩马一啸咏之地。无不起书院崇奉。则吾乡之于两先生。其可无其祠乎。先辈之所以立院宇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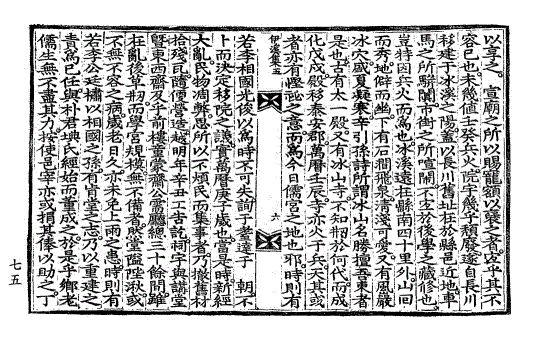 以享之。 宣庙之所以赐宠额以褒之者。宜乎其不容已也。未几值壬癸兵火。院宇几乎颓废。遂自长川移建于冰溪之阳。盖以长川旧址在于县邑近地。车马之所骈阗。市街之所喧闹。不宜于后学之藏修也。岂特因兵火而为也。冰溪远在县南四十里外。山回而秀。地僻而幽。下有石涧飞泉。清浅可爱。又有风岩冰穴。盛夏凝寒。辛引孙诗所谓冰山名胜擅吾东者是也。古有太一殿。又有冰山寺。不知刱于何代。而成化戊戌。殿移泰安郡。万历壬辰。寺亦火于兵。天其或者亦有悭秘之意。而为今日儒宫之地也邪。时则有若李相国光俊以为时不可失。询于耋达于 朝。不卜而决定移院之议。实万历庚子岁也。当是时。新经大乱。民物凋弊。思所以不烦民而集事者。乃撤旧材拾残瓦。随便营造。越明年辛丑工告讫。祠宇与讲堂暨东西斋及乎前楼童蒙斋公需厅总三十馀间。虽在乱后草刱。而学宫规模。无不备者。然堂隘陛湫。或不无不容之病。岁老日久。亦未免上雨之患。时则有若李公廷橚以相国之孙。有肯堂之志。乃以重建之责为己任。与朴君腆氏经始而董成之。于是乎乡老儒生无不尽其力。按使邑宰亦或捐其俸以助之。丁
以享之。 宣庙之所以赐宠额以褒之者。宜乎其不容已也。未几值壬癸兵火。院宇几乎颓废。遂自长川移建于冰溪之阳。盖以长川旧址在于县邑近地。车马之所骈阗。市街之所喧闹。不宜于后学之藏修也。岂特因兵火而为也。冰溪远在县南四十里外。山回而秀。地僻而幽。下有石涧飞泉。清浅可爱。又有风岩冰穴。盛夏凝寒。辛引孙诗所谓冰山名胜擅吾东者是也。古有太一殿。又有冰山寺。不知刱于何代。而成化戊戌。殿移泰安郡。万历壬辰。寺亦火于兵。天其或者亦有悭秘之意。而为今日儒宫之地也邪。时则有若李相国光俊以为时不可失。询于耋达于 朝。不卜而决定移院之议。实万历庚子岁也。当是时。新经大乱。民物凋弊。思所以不烦民而集事者。乃撤旧材拾残瓦。随便营造。越明年辛丑工告讫。祠宇与讲堂暨东西斋及乎前楼童蒙斋公需厅总三十馀间。虽在乱后草刱。而学宫规模。无不备者。然堂隘陛湫。或不无不容之病。岁老日久。亦未免上雨之患。时则有若李公廷橚以相国之孙。有肯堂之志。乃以重建之责为己任。与朴君腆氏经始而董成之。于是乎乡老儒生无不尽其力。按使邑宰亦或捐其俸以助之。丁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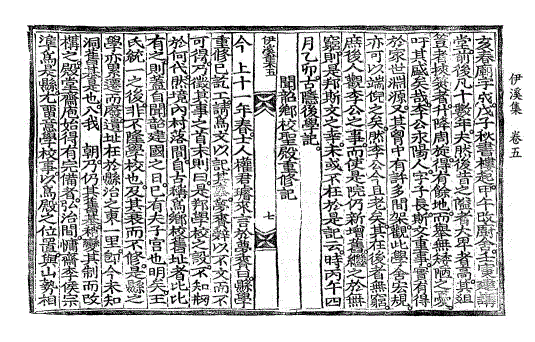 亥春庙宇成。戊子秋书楼起。甲午改厨舍。壬寅建讲堂。前后凡十数年。夫然后昔之隘者大卑者高。其俎豆者挟筴者。升降周旋。得有馀地。而举无矮陋之忧。吁其盛矣哉。李公永阳人。字子长。斯文重事。实有得于家世渊源。又其胸中有许多间架。观此学舍宏规。亦可以端倪之矣。然李公今且老矣。其在后者无穷。庶后人观李公之事。而使是院仍新增旧。继之于无穷。则是邦斯文之幸。未或不在于是记云。时丙午四月乙卯。古隐后学记。
亥春庙宇成。戊子秋书楼起。甲午改厨舍。壬寅建讲堂。前后凡十数年。夫然后昔之隘者大卑者高。其俎豆者挟筴者。升降周旋。得有馀地。而举无矮陋之忧。吁其盛矣哉。李公永阳人。字子长。斯文重事。实有得于家世渊源。又其胸中有许多间架。观此学舍宏规。亦可以端倪之矣。然李公今且老矣。其在后者无穷。庶后人观李公之事。而使是院仍新增旧。继之于无穷。则是邦斯文之幸。未或不在于是记云。时丙午四月乙卯。古隐后学记。闻韶乡校圣殿重修记
今 上十一年春。士人权君璿来言于梦赉曰。县学重修已讫工。请为文以记其事。梦赉辞以不文而不可得。乃徵其事之首末则曰。是邦学校之设。不知刱于何代。然境内村落间。自古称为乡校旧址者比比有之。则盖自闻韶建国之日。已有夫子宫也明矣。王氏统一之后。非不隆学校也。及其衰而不修。是县之学亦累迁而废。遗址在于县治之东一里。即今未知洞旧基是也。入我 朝。乃仍其旧基。稍变其制而改构之。殿堂斋庖始得有完备者。弘治间。慵斋李侯宗准为是县。尤留意学校事。以为殿之位置。与山势相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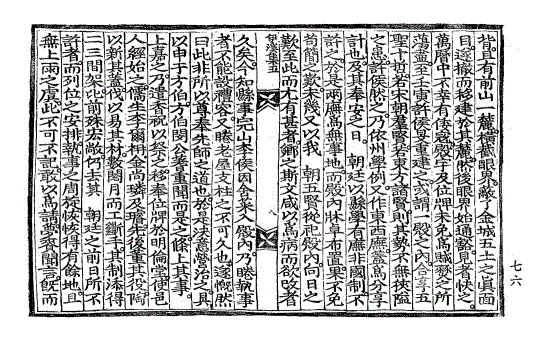 背。且有前山一麓。横截眼界。蔽了金城五土之真面目。遂撤而移建于其麓。然后眼界始通豁。见者快之。万历中不幸有倭寇。殿宇及位牌未免为贼燹之所荡尽。至壬寅许侯旻重建之。或谓一殿之内。合享五圣十哲。若宋朝群贤。若东方诸贤。则其势不无狭隘之患。许侯然之。乃依州学例。又作东西庑。盖为分享计也。及其奉安之日。 朝廷以县学有庑非国制。不许之。于是两庑为无事地。而殿内床卓布置。果不免苟简之叹。未几又以我 朝五贤从祀殿内。向日之叹至此而尤有甚者。乡之斯文咸以为病而欲改者久矣。今知县事完山李侯因舍菜入殿内。乃眷执事者不能设礼容。又眷老屋支柱之不可久也。遂慨然曰此非所以尊奉先师之道也。于是决意营治之。具以申于方伯。方伯闵公蓍重闻而是之。条上其事。 上嘉之。乃遣香祝以祭之。移奉位牌于明伦堂。使邑人经始之。儒生李尔楠,金尚璘及璿。先后董其役。陶以新其盖。伐以易其材。数阅月而工断手。其制添得二三间架。比前殊宏敞。仍去其 朝廷之前日所不许者。而列位之安排。执事之周旋。恢恢得有馀地。且无上雨之虞。此不可不记。敢以为请。梦赉闻言。既而
背。且有前山一麓。横截眼界。蔽了金城五土之真面目。遂撤而移建于其麓。然后眼界始通豁。见者快之。万历中不幸有倭寇。殿宇及位牌未免为贼燹之所荡尽。至壬寅许侯旻重建之。或谓一殿之内。合享五圣十哲。若宋朝群贤。若东方诸贤。则其势不无狭隘之患。许侯然之。乃依州学例。又作东西庑。盖为分享计也。及其奉安之日。 朝廷以县学有庑非国制。不许之。于是两庑为无事地。而殿内床卓布置。果不免苟简之叹。未几又以我 朝五贤从祀殿内。向日之叹至此而尤有甚者。乡之斯文咸以为病而欲改者久矣。今知县事完山李侯因舍菜入殿内。乃眷执事者不能设礼容。又眷老屋支柱之不可久也。遂慨然曰此非所以尊奉先师之道也。于是决意营治之。具以申于方伯。方伯闵公蓍重闻而是之。条上其事。 上嘉之。乃遣香祝以祭之。移奉位牌于明伦堂。使邑人经始之。儒生李尔楠,金尚璘及璿。先后董其役。陶以新其盖。伐以易其材。数阅月而工断手。其制添得二三间架。比前殊宏敞。仍去其 朝廷之前日所不许者。而列位之安排。执事之周旋。恢恢得有馀地。且无上雨之虞。此不可不记。敢以为请。梦赉闻言。既而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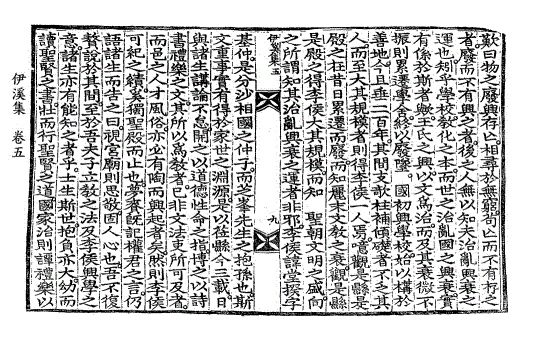 叹曰物之废兴存亡。相寻于无穷。苟亡而不有存之者。废而不有兴之者。后之人无以知夫治乱兴衰之运也。矧乎学校。教化之本。而世之治乱国之兴衰。实有系于斯者欤。王氏之兴。以文为治。而及其衰微不振则累迁学舍。终以废坠。 国初兴学校。始以构于善地。今且垂二百年。其间支欹柱补倾础者不乏其人。而至大其规模者则得李侯一人焉。噫观是县是殿之在昔日累迁而废。而知丽末文教之衰。观是县是殿之得李侯大其规模。而知 圣朝文明之盛。向之所谓知其治乱兴衰之运者非邪。李侯讳堂揆字基仲。是分沙相国之仲子。而芝峰先生之抱孙也。斯文重事实有得于家世之渊源。是以莅县今三载。日与诸生讲论不怠。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其所以为教者。已非文法吏所可及者。而邑之人才风俗。亦必有陶而兴起者矣。然则李侯可纪之绩。奚独圣殿而止也。梦赉既记权君之言。仍语诸生而告之曰。视宫庙则思敬。固人心也。吾不复赘说于其间。至于吾夫子立教之法及李侯兴学之意。诸生亦有能知之者乎。士生斯世。抱负亦大。幼而读圣贤之书。壮而行圣贤之道。国家治则谭礼乐以
叹曰物之废兴存亡。相寻于无穷。苟亡而不有存之者。废而不有兴之者。后之人无以知夫治乱兴衰之运也。矧乎学校。教化之本。而世之治乱国之兴衰。实有系于斯者欤。王氏之兴。以文为治。而及其衰微不振则累迁学舍。终以废坠。 国初兴学校。始以构于善地。今且垂二百年。其间支欹柱补倾础者不乏其人。而至大其规模者则得李侯一人焉。噫观是县是殿之在昔日累迁而废。而知丽末文教之衰。观是县是殿之得李侯大其规模。而知 圣朝文明之盛。向之所谓知其治乱兴衰之运者非邪。李侯讳堂揆字基仲。是分沙相国之仲子。而芝峰先生之抱孙也。斯文重事实有得于家世之渊源。是以莅县今三载。日与诸生讲论不怠。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其所以为教者。已非文法吏所可及者。而邑之人才风俗。亦必有陶而兴起者矣。然则李侯可纪之绩。奚独圣殿而止也。梦赉既记权君之言。仍语诸生而告之曰。视宫庙则思敬。固人心也。吾不复赘说于其间。至于吾夫子立教之法及李侯兴学之意。诸生亦有能知之者乎。士生斯世。抱负亦大。幼而读圣贤之书。壮而行圣贤之道。国家治则谭礼乐以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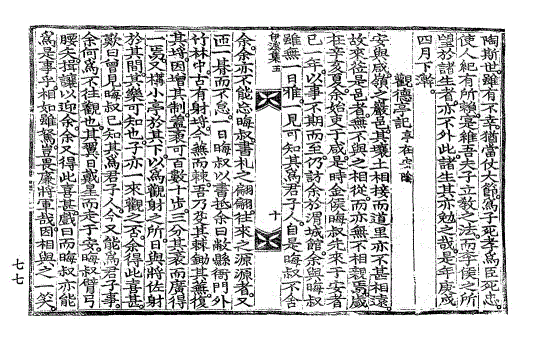 陶斯世。虽有不幸。犹当仗大节。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使人纪有所赖。寔维吾夫子立教之法。而李侯之所望于诸生者。亦不外此。诸生其亦勉之哉。是年庚戌四月下浣。
陶斯世。虽有不幸。犹当仗大节。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使人纪有所赖。寔维吾夫子立教之法。而李侯之所望于诸生者。亦不外此。诸生其亦勉之哉。是年庚戌四月下浣。观德亭记(亭在安阴)
安与咸。岭之岩邑。其壤土相接而道里亦不甚相远。故来莅是邑者。无不与之相从。而亦无不相亲焉。岁在辛亥夏。余始吏于咸。是时金侯晦叔先来于安者已一年。以事不期而至。仍访余于渭城馆。余与晦叔虽无一日雅。一见可知其为君子人。自是晦叔不舍余。余亦不能忘晦叔。书札之翩翩。往来之源源者。又匝一期而不怠。一日晦叔以书抵余曰敝县衙门外竹林中。古有射埒。今芜而棘。吾乃芟其棘锄其芜。复其埒。因增其制。盖袤可百数十步。三分其袤而广得一焉。又构小亭于其下。以为观射之所。日与将佐射于其间。其乐可知也。子亦一来观之否。余得此喜甚。叹曰曾见晦叔已知其为君子人。今又能为君子事。余何为不往观也。其翼日戴星而走于安。晦叔臂弓腰矢。揖让以迎余。余又得此喜甚。戏曰而晦叔亦能为是事乎。相如虽驽。岂畏廉将军哉。因相与之一笑。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8H 页
 而又与之为一耦。终日射侯以相乐也。临罢余谓晦叔曰子既能为是事。亦能知夫是义乎。一自挥夷牟之后。弧矢为男子之所有事者尚矣。三代之所尚。六艺之所取。而经传之所记述。班班亦可考也。无事则升降周旋。进退雍容。月满星流。下留上扬而可以观德行。有事则电掣风生。左马右人。繇胊汰辀。洞胸穿甲而可以御㬥乱。无非事者。事之大者。孰有大于是也。是以古之人。或以射为君子之事。或以仁者比射之德焉。语其体也。持弓矢审固。正己而后发而心以之正。语其用也。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功成而德行立。无㬥乱之祸而国以之安。此所以为德行之艺。而君子之所不可已者也。昔吾夫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序点又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者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然则射之之义。又有大于大者。而其责之于人者。不亦重且厚矣乎。今吾与子幸而生于天命日新之日。而又值 圣上神武之运。则贲军之累。亡国之羞。非所可论。而又幸而生于小华礼义之邦。又得闻
而又与之为一耦。终日射侯以相乐也。临罢余谓晦叔曰子既能为是事。亦能知夫是义乎。一自挥夷牟之后。弧矢为男子之所有事者尚矣。三代之所尚。六艺之所取。而经传之所记述。班班亦可考也。无事则升降周旋。进退雍容。月满星流。下留上扬而可以观德行。有事则电掣风生。左马右人。繇胊汰辀。洞胸穿甲而可以御㬥乱。无非事者。事之大者。孰有大于是也。是以古之人。或以射为君子之事。或以仁者比射之德焉。语其体也。持弓矢审固。正己而后发而心以之正。语其用也。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功成而德行立。无㬥乱之祸而国以之安。此所以为德行之艺。而君子之所不可已者也。昔吾夫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序点又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者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然则射之之义。又有大于大者。而其责之于人者。不亦重且厚矣乎。今吾与子幸而生于天命日新之日。而又值 圣上神武之运。则贲军之累。亡国之羞。非所可论。而又幸而生于小华礼义之邦。又得闻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8L 页
 先生长者之绪论。则虽使生于夫子之世。或不在去者之列。此吾与子之所加勉者。今日之会。亦岂为閒追逐也。虽然胜地不常。盛事难再。及其情随事迁之后。崇山峻岭。茂林脩竹。未或不为右军兴怀之地。则其可使之没没无传而遂已也邪。于是晦叔闻言而喜。既而持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射。三发连三中。观者连三大呼笑。乃名是亭曰观德亭。仍使画工为之图而属余记。时壬子五月竹醉日。英阳南梦赉记。
先生长者之绪论。则虽使生于夫子之世。或不在去者之列。此吾与子之所加勉者。今日之会。亦岂为閒追逐也。虽然胜地不常。盛事难再。及其情随事迁之后。崇山峻岭。茂林脩竹。未或不为右军兴怀之地。则其可使之没没无传而遂已也邪。于是晦叔闻言而喜。既而持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射。三发连三中。观者连三大呼笑。乃名是亭曰观德亭。仍使画工为之图而属余记。时壬子五月竹醉日。英阳南梦赉记。春窝记
余吏天岭。得梁生锡蕃之为人而信爱之久也。一日生请于余曰蕃筑一书室于敝庐之侧。翳蓬藋而居焉。适其成在于春。故名之曰春窝。惟夫子为知蕃之志。敢请为春之说。幸以教之。则蕃之愿也。余辞谢不获。仍念余与生相接。于今几一年。视其学。盖专用力于仁者。而世之所谓粗厉鄙倍之气。不以介于其间。尝窃以为生之学。有若有志乎颜子之春生。程氏之春风者然。是以爱之深而信之笃也。及闻其名斋之说则益信其前所信者。余于吾子之志。不可谓之不知。然必欲语子以为春之说则是说也。吾子既自知之。余又奚以语。吾子抑尝闻之。夫春也者。天地生物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9H 页
 之心而人之所得而为仁者也。即所谓心之德者是已。是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之德无所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亦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者也。然而人有是身则不能无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未或不为害夫仁者。若不克而去之。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无所不至。此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不过去其害仁者而已。颜子之所以克己复礼。程氏之所以窒欲用敬者。何莫非去其害求是理之功也。而去之益力。求之益久。一朝至于浑然融液。欲尽理纯之域。则其胸中之所存者。粹然合于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有春阳之温者。安可诬也。今者吾子之居是窝也。必有事焉。而其所以诵法者。一则颜程。二则颜程。则颜子之春。程氏之春。其亦庶几焉。窥测其气像而犹恐造次之或遗。遂以春名其室。则其于所以求仁之方。可谓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为也。况吾子继自今必将因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知者。虽在食息跬步之间。念玆在玆。无或息焉。驯而至于至善之地。则夫所谓春者。亦必有盎
之心而人之所得而为仁者也。即所谓心之德者是已。是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之德无所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亦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者也。然而人有是身则不能无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未或不为害夫仁者。若不克而去之。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无所不至。此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不过去其害仁者而已。颜子之所以克己复礼。程氏之所以窒欲用敬者。何莫非去其害求是理之功也。而去之益力。求之益久。一朝至于浑然融液。欲尽理纯之域。则其胸中之所存者。粹然合于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有春阳之温者。安可诬也。今者吾子之居是窝也。必有事焉。而其所以诵法者。一则颜程。二则颜程。则颜子之春。程氏之春。其亦庶几焉。窥测其气像而犹恐造次之或遗。遂以春名其室。则其于所以求仁之方。可谓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为也。况吾子继自今必将因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知者。虽在食息跬步之间。念玆在玆。无或息焉。驯而至于至善之地。则夫所谓春者。亦必有盎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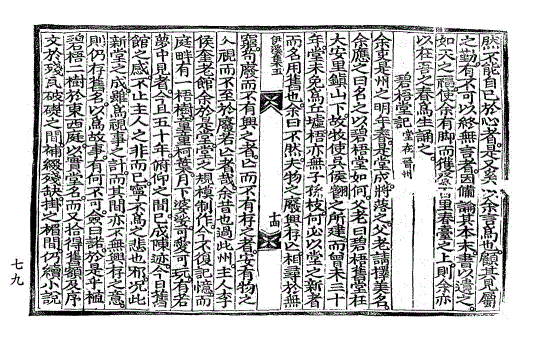 然不能自已于心者。是又奚以余言为也。顾其见属之勤。有不可以终无言者。因备论其本末。书以遗之。如天之福。使余有脚而获登百里春台之上。则余亦以在吾之春为生诵之。
然不能自已于心者。是又奚以余言为也。顾其见属之勤。有不可以终无言者。因备论其本末。书以遗之。如天之福。使余有脚而获登百里春台之上。则余亦以在吾之春为生诵之。碧梧堂记(堂在晋州)
余吏是州之明年春。是堂成。将落之。父老请择美名。余应之曰名之以碧梧堂如何。父老曰碧梧旧堂在大安里镇山下。故牧使吴侯䎙之所建。而曾未三十年。堂未免为丘墟。梧亦无子孙枝。何必以堂之新者而名用旧也。余曰不然。夫物之废兴存亡。相寻于无穷。苟废而不有兴之者。亡而不有存之者。安有物之久视而不至于废若亡者哉。余昔也过此州。主人李侯奎老馆余于是堂。堂之规模制作。今不复记忆。而庭畔有一梧树。童童柯叶。月下婆娑。可爱可玩。有若梦中见者。今且五十年。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今日旧馆之感。不止主人之非而已。宁不为之悲也邪。况此新堂之成。虽为视事之计。而其间亦不无兴存之意。则仍存旧名。以为故事。有何不可。佥曰诺。于是乎植碧梧二树于东西庭。以实堂名。而又拾得旧额及序文于残瓦破础之间。补缀残缺。挂之楣间。仍续小说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0H 页
 于其后。以备后之览者云。时甲寅正月既望。牧使南梦赉记。
于其后。以备后之览者云。时甲寅正月既望。牧使南梦赉记。茅山亭记
茅山在花山府北十数里。古有隐君子居焉。其下盖有茅山亭云。亭之主人金君鼎基氏。一日过余于伊溪。仍语余曰茅山是鼎基之外曾大父药圃郑先生旧居也。先生移卜岘山之后。思之独不置。然卒不得归。则临殁始析而与其子孙。鼎基之先君子复以数缗山钱易而居之。仍构数椽小亭于山下。命名曰茅山。以为修道游息之地亦有年矣。鼎基不幸生未晬而慈母见背。又未几而先君子大归川庄。又未几而奄弃诸孤。惟其独立而岿然者。未免为山中一空舍。鼎基之兄弟为是惧。使鼎基来居是亭。今且近十年。贫病苟活。虽不能大其门闾。以承先志。然犹自乐其所由生。不敢忘先世遗训。则敬以先君子所尝命名于亭者。嘱李斯文观徵而大书之。揭之亭壁。以寓夙夜虔省之目。又欲略记先训不敢忘之意。以示之子孙而使之有所考焉。子其为我记之。余以不文辞。金君犹强之不已。即亦不可终以辞辞。遂起而为之说曰。世之为人子孙而承先世基业者。孰不愿为之毋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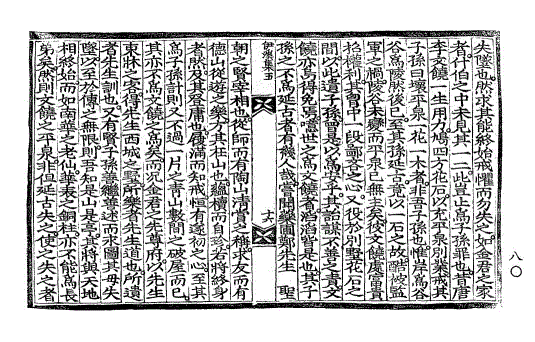 失坠也。然求其能终始戒惧而勿失之。如金君之家者。什伯之中未见其一二。此岂止为子孙罪也。昔唐李文饶一生用力。鸠四方花石。以充平泉别业。戒其子孙曰坏平泉一花一木者。非吾子孙也。惟岸为谷谷为陵然后已。至其孙延古。竟以一石之故。酷被监军之祸。陵谷未变而平泉已无主矣。彼文饶处富贵招权利。其胸中一段鄙吝之心。又役于别墅花石之间。以此遗子孙。曾是以为安乎。其诒谋不善之责。文饶亦乌得免焉。噫世之为文饶者。滔滔皆是也。其子孙之不为延古者有几人哉。尝闻药圃郑先生 圣朝之贤宰相也。从师而有陶山清赏之称。求友而有德山从游之乐。方其在山也。蕴椟而自珍。若将终身者然。及其登庸也。履满而知戒。恒有遂初之心。至其为子孙计则又不过一片之青山数间之破屋而已。其亦不为文饶之为矣。而况金君之先尊府。以先生东床之客。得先生西城之墅。所乐者先生道也。所遗者先生训也。又有贤子孙善继善述而永图其毋失坠。以至于传之无限。则吾知是山是亭。其将与天地相终始。而如南华之老仙。华表之铜柱。亦不能为长弟矣。然则文饶之平泉。非但延古失之。使之失之者
失坠也。然求其能终始戒惧而勿失之。如金君之家者。什伯之中未见其一二。此岂止为子孙罪也。昔唐李文饶一生用力。鸠四方花石。以充平泉别业。戒其子孙曰坏平泉一花一木者。非吾子孙也。惟岸为谷谷为陵然后已。至其孙延古。竟以一石之故。酷被监军之祸。陵谷未变而平泉已无主矣。彼文饶处富贵招权利。其胸中一段鄙吝之心。又役于别墅花石之间。以此遗子孙。曾是以为安乎。其诒谋不善之责。文饶亦乌得免焉。噫世之为文饶者。滔滔皆是也。其子孙之不为延古者有几人哉。尝闻药圃郑先生 圣朝之贤宰相也。从师而有陶山清赏之称。求友而有德山从游之乐。方其在山也。蕴椟而自珍。若将终身者然。及其登庸也。履满而知戒。恒有遂初之心。至其为子孙计则又不过一片之青山数间之破屋而已。其亦不为文饶之为矣。而况金君之先尊府。以先生东床之客。得先生西城之墅。所乐者先生道也。所遗者先生训也。又有贤子孙善继善述而永图其毋失坠。以至于传之无限。则吾知是山是亭。其将与天地相终始。而如南华之老仙。华表之铜柱。亦不能为长弟矣。然则文饶之平泉。非但延古失之。使之失之者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1H 页
 文饶也。药圃之茅山。非但子孙保之。使之保之者药圃也。世之为人祖为人子孙者。亦可以知所劝戒之矣。金君其亦加勉之哉。岁在著雍敦牂三月壬辰。伊溪散人记。
文饶也。药圃之茅山。非但子孙保之。使之保之者药圃也。世之为人祖为人子孙者。亦可以知所劝戒之矣。金君其亦加勉之哉。岁在著雍敦牂三月壬辰。伊溪散人记。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跋
书温泉扈 驾时画屏题名记后
岁在丁未春。 车驾行幸温阳之汤井。于是判书金公以整理使先往。参判李公以副总管扈 驾。梦赉以兼官备左史从焉。在 行宫数十日而回 驾。是时吾 王庶几无疾病。陪从百僚举欣欣然有喜色。往往于屏簇上列书其名而记其事。判书公仍命工作三屏。而梦赉亦得其一焉。置之京邸。久未载来。甲寅秋邸吏因州吏入城者。附送于晋阳任所。捧展未既。悲感先集。盖于今年八月己酉。 圣考已捐群臣矣。追思往事。恍然如昨。而瞻望云天。 弓剑莫攀。未死孤臣。当作何如怀也邪。谨识下方。以寓无涯之恸云。时甲寅十月朔辛卯。通训大夫晋州牧使晋州镇兵马佥节制使。臣南梦赉涕泣谨书。
题丧服考證后
夫得天之经合地之义而为生民之秉彝者。君臣父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1L 页
 子之大伦是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事之以礼。死则尊之以礼者。夫岂虚加之也。诚以不如是则无以致吾忠孝之心耳。 国家己亥之夏。臣民无禄。天降大割。率土同戚。 弓剑莫攀。为其臣子者惟当思所以尊之以礼。致吾忠孝之为无憾。而其时议礼之臣。敢为背礼不经之说。乃以四种服制中体而不正之庶子。诬我 先王而贬降之。不许以宗嫡之统。而使 大王大妃不得为长子之服。以至今日。 孝庙在天之灵。终抱被诬见贬之痛而不安于 陟降之位。 圣上仁孝之诚。犹有所憾于尊亲之礼。而恒怀哀疚之心。臣子之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伸其冤者。曷有穷哉。盖其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实有天赋之所同得者。未死则当辨。未辨则当死。不可苟焉而已也。噫今日在廷之臣。曷尝有为为 先王伸辨之说者哉。当初议礼时。许眉翁一二人外。于今十馀年之久而寂寂无闻于侍从之列。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果安在哉。曾在甲辰乙巳间。前县监柳公元之以是录示余。仍泣数行下曰一时服制紊乱之失。虽曰不谏。万世嫡庶斩截之统。不可不正。吾欲以是录冒渎 宸严。为 先王一死。余受
子之大伦是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事之以礼。死则尊之以礼者。夫岂虚加之也。诚以不如是则无以致吾忠孝之心耳。 国家己亥之夏。臣民无禄。天降大割。率土同戚。 弓剑莫攀。为其臣子者惟当思所以尊之以礼。致吾忠孝之为无憾。而其时议礼之臣。敢为背礼不经之说。乃以四种服制中体而不正之庶子。诬我 先王而贬降之。不许以宗嫡之统。而使 大王大妃不得为长子之服。以至今日。 孝庙在天之灵。终抱被诬见贬之痛而不安于 陟降之位。 圣上仁孝之诚。犹有所憾于尊亲之礼。而恒怀哀疚之心。臣子之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伸其冤者。曷有穷哉。盖其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实有天赋之所同得者。未死则当辨。未辨则当死。不可苟焉而已也。噫今日在廷之臣。曷尝有为为 先王伸辨之说者哉。当初议礼时。许眉翁一二人外。于今十馀年之久而寂寂无闻于侍从之列。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果安在哉。曾在甲辰乙巳间。前县监柳公元之以是录示余。仍泣数行下曰一时服制紊乱之失。虽曰不谏。万世嫡庶斩截之统。不可不正。吾欲以是录冒渎 宸严。为 先王一死。余受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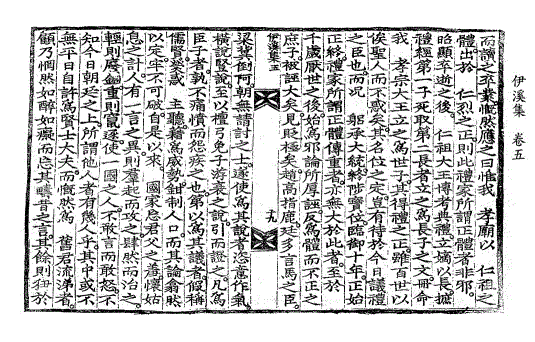 而读之卒业。慨然应之曰惟我 孝庙以 仁祖之体。出于 仁烈之正。则此礼家所谓正体者非邪。 昭显卒逝之后。 仁祖大王博考典礼。立嫡以长。摭礼经第一子死取第二长者立之为长子之文。册命我 孝宗大王立之为世子。其得礼之正。虽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矣。其名位之定。岂有待于今日议礼之臣也。而况 躬承大统。终陟宝位。临御十年。正始正终。礼家所谓正体传重者。亦无大于此者。至于 千岁厌世之后。始为邪论所厚诬。反为体而不正之庶子。被诬大矣。见贬极矣。赵高指鹿。廷多言马之臣。梁冀倒阿。朝无请讨之士。遂使为其说者恣意作气。横说竖说。至以檀弓免子游衰之说。引而證之。凡为臣子者。孰不痛愤而怨疾之也。第以为其议者。假称儒贤。荧惑 主听。藉为威势。钳制人口。而其论翕然以定。牢不可破。自是以来。 国家忘君父之羞。怀姑息之计。人有一言之异。则群起而攻之。肆然而治之。轻则废锢。重则窜逐。使一国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不知今日朝廷之上。所谓他人者有几人乎。其中或不无平日自许为贤士大夫。而慨然为 旧君流涕者。顾乃惘然如醉如痴而忘其畴昔之言。其馀则狃于
而读之卒业。慨然应之曰惟我 孝庙以 仁祖之体。出于 仁烈之正。则此礼家所谓正体者非邪。 昭显卒逝之后。 仁祖大王博考典礼。立嫡以长。摭礼经第一子死取第二长者立之为长子之文。册命我 孝宗大王立之为世子。其得礼之正。虽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矣。其名位之定。岂有待于今日议礼之臣也。而况 躬承大统。终陟宝位。临御十年。正始正终。礼家所谓正体传重者。亦无大于此者。至于 千岁厌世之后。始为邪论所厚诬。反为体而不正之庶子。被诬大矣。见贬极矣。赵高指鹿。廷多言马之臣。梁冀倒阿。朝无请讨之士。遂使为其说者恣意作气。横说竖说。至以檀弓免子游衰之说。引而證之。凡为臣子者。孰不痛愤而怨疾之也。第以为其议者。假称儒贤。荧惑 主听。藉为威势。钳制人口。而其论翕然以定。牢不可破。自是以来。 国家忘君父之羞。怀姑息之计。人有一言之异。则群起而攻之。肆然而治之。轻则废锢。重则窜逐。使一国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不知今日朝廷之上。所谓他人者有几人乎。其中或不无平日自许为贤士大夫。而慨然为 旧君流涕者。顾乃惘然如醉如痴而忘其畴昔之言。其馀则狃于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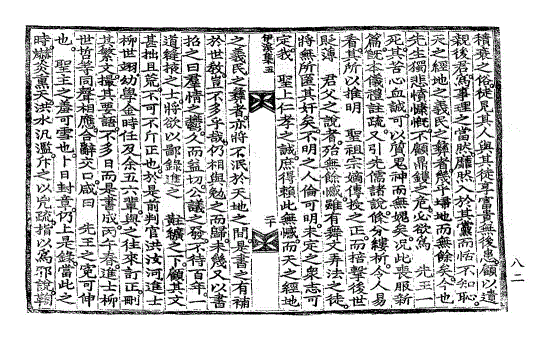 积衰之俗。徒见其人与其徒享富贵无后患。顾以遗亲后君。为事理之当然。靡然入于其党而恬不知耻。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几乎埽地而无馀矣。今也先生独悲愤慷慨。不顾鼎镬之危。必欲为 先王一死。其苦心血诚。可以质鬼神而无愧矣。况此丧服新篇。既本仪礼注疏。又引先儒诸说。条分缕析。令人易看。其所以推明 圣祖宗嫡传授之正。而掊击后世贬薄 君父之说者。殆无馀憾。虽有舞文弄法之徒。将无所匿其奸矣。不明之人伦可明。未定之众志可定。我 圣上仁孝之诚。庶得赖此无憾。而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亦将不泯于天地之间。是书之有补于世教。岂不多乎哉。仍相与勉之而归。未几又以书招之曰群情之郁。久而益切。公议之发。不待百年。一道缝掖之士。将欲以鄙录进之 黈纩之下。顾其文甚拙且荒。不可不斤正也。于是前判官洪汝河,进士柳世翊,幼学金时任及余五六辈。与之往来订正。删其繁文。撮其要语。不多日而是书成。丙午春。进士柳世哲等同声相应。合辞交口。咸曰 先王之冤可伸也。 圣主之羞可雪也。卜日封章。仍上是录。当此之时。赫炎熏天。洪水汎滥。斥之以凶疏。指以为邪说。鞫
积衰之俗。徒见其人与其徒享富贵无后患。顾以遗亲后君。为事理之当然。靡然入于其党而恬不知耻。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几乎埽地而无馀矣。今也先生独悲愤慷慨。不顾鼎镬之危。必欲为 先王一死。其苦心血诚。可以质鬼神而无愧矣。况此丧服新篇。既本仪礼注疏。又引先儒诸说。条分缕析。令人易看。其所以推明 圣祖宗嫡传授之正。而掊击后世贬薄 君父之说者。殆无馀憾。虽有舞文弄法之徒。将无所匿其奸矣。不明之人伦可明。未定之众志可定。我 圣上仁孝之诚。庶得赖此无憾。而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亦将不泯于天地之间。是书之有补于世教。岂不多乎哉。仍相与勉之而归。未几又以书招之曰群情之郁。久而益切。公议之发。不待百年。一道缝掖之士。将欲以鄙录进之 黈纩之下。顾其文甚拙且荒。不可不斤正也。于是前判官洪汝河,进士柳世翊,幼学金时任及余五六辈。与之往来订正。删其繁文。撮其要语。不多日而是书成。丙午春。进士柳世哲等同声相应。合辞交口。咸曰 先王之冤可伸也。 圣主之羞可雪也。卜日封章。仍上是录。当此之时。赫炎熏天。洪水汎滥。斥之以凶疏。指以为邪说。鞫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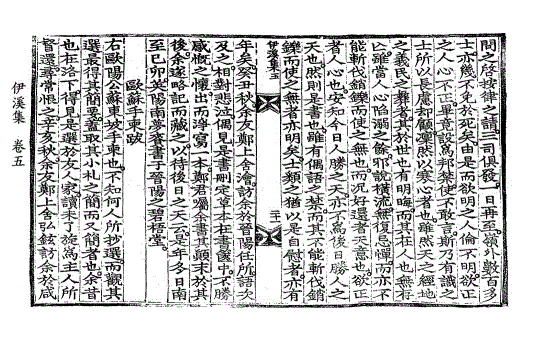 问之启按律之请。三司俱发。一日再至。岭外数百多士。亦几不免于死矣。由是而欲明之人伦不明。欲正之人心不正。毕竟设为邦禁。使不敢言。斯乃有识之士所以长虑却顾。凛然以寒心者也。虽然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其于世也有明晦。而其在人也无存亡。虽当人心陷溺之馀。邪说横流。无复忌惮。而亦不能斩伐销铄而使之无也。而况好还者天意也。欲正者人心也。安知今日人胜之天。亦不为后日胜人之天也。然则是书也。虽有偶语之禁。而其不能斩伐销铄而使之无者亦明矣。士类之犹以是自慰者。亦有年矣。癸丑秋。余友郑上舍浍。访余于晋阳任所。语次及之。相对悲泣。偶见是书删定草本在书箧中。不胜感慨之怀。出而净写一本。郑君嘱余书其颠末于其后。余遂略记而藏之。以待后日之天云。是年冬日南至己卯。英阳南梦赉书于晋阳之碧梧堂。
问之启按律之请。三司俱发。一日再至。岭外数百多士。亦几不免于死矣。由是而欲明之人伦不明。欲正之人心不正。毕竟设为邦禁。使不敢言。斯乃有识之士所以长虑却顾。凛然以寒心者也。虽然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彝者。其于世也有明晦。而其在人也无存亡。虽当人心陷溺之馀。邪说横流。无复忌惮。而亦不能斩伐销铄而使之无也。而况好还者天意也。欲正者人心也。安知今日人胜之天。亦不为后日胜人之天也。然则是书也。虽有偶语之禁。而其不能斩伐销铄而使之无者亦明矣。士类之犹以是自慰者。亦有年矣。癸丑秋。余友郑上舍浍。访余于晋阳任所。语次及之。相对悲泣。偶见是书删定草本在书箧中。不胜感慨之怀。出而净写一本。郑君嘱余书其颠末于其后。余遂略记而藏之。以待后日之天云。是年冬日南至己卯。英阳南梦赉书于晋阳之碧梧堂。欧苏手柬跋
右欧阳公苏东坡手柬也。不知何人所抄选。而观其选最得其简要。盖取其小札之简而又简者也。余昔也在洛下。得见是选于友人家。读未了旋为主人所督还。寻常恨之。辛亥秋。余友郑上舍弘铉访余于咸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3L 页
 阳任所。袖是选以示余。宛然有旧日颜面。爱玩之不已。藏之巾笥而不敢释。欲与好之者共之。则谋所以广其传者。而又恨其力不逮也。及至晋阳。适有阳村文集重刊之役。仍属剞劂氏入之梓。欧凡四十九。苏凡九十五。共百四十四。或嫌其太少。余应之曰奚以多为也。折俎虽不及体荐。拣金亦必待淘沙。是亦文苑一例。奚以多为也。或然其言。使余记其颠末。非敢有所评论于其间云。岁甲寅三月朔。英阳南梦赉识。
阳任所。袖是选以示余。宛然有旧日颜面。爱玩之不已。藏之巾笥而不敢释。欲与好之者共之。则谋所以广其传者。而又恨其力不逮也。及至晋阳。适有阳村文集重刊之役。仍属剞劂氏入之梓。欧凡四十九。苏凡九十五。共百四十四。或嫌其太少。余应之曰奚以多为也。折俎虽不及体荐。拣金亦必待淘沙。是亦文苑一例。奚以多为也。或然其言。使余记其颠末。非敢有所评论于其间云。岁甲寅三月朔。英阳南梦赉识。题宋氏家藏契帖后
右冶垆宋氏家藏。其先祖上舍公与寒暄金先生及诸名胜修契之帖也。近世鹤沙金公金斯文天休父相继为跋语。已具道其颠末。而上舍之四世孙宋君光璧氏出而示之余。而又使之题其后。噫宋君之意不亦近于赘之甚者邪。况余晚生。其于先辈事迹。复何能有所发明。但计景泰庚子距今辛亥凡几年。甲子又几周乎。帖中诸贤虽已骨朽。然百年之后。犹有此不泯者存焉。又其子孙尚能奉守而揄扬之。彼一时之潝潝訾訾者。果安在哉。嗟叹之不足。姑窃识其左方。四月八日。后学南梦赉书于洛阳二桥之寓舍。
书家牒后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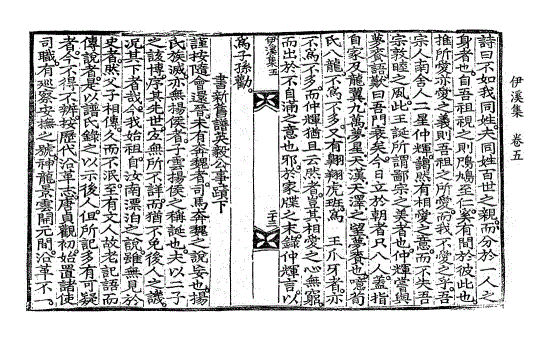 诗曰不如我同姓。夫同姓百世之亲。而分于一人之身者也。自吾祖视之则鸤鸠至仁。奚有间于彼此也。推所爱亦爱之义则吾祖之所爱。而我不爱之乎。吾宗人南舍人二星仲辉。蔼然有相爱之意。而不失吾宗敦睦之风。此王诞所谓鄙宗之美者也。仲辉尝与梦赉语。叹曰吾门衰矣。今日立于朝者只八人。盖指自家及龙翼,九万,梦星,天汉,天泽,之望,梦赉也。噫荀氏八龙。不为不多。又有翱翔虎班。为 王爪牙者。亦不为不多。而仲辉犹且云然者。岂其相爱之心无穷。而出于不自满之意也邪。于家牒之末。录仲辉言。以为子孙劝。
诗曰不如我同姓。夫同姓百世之亲。而分于一人之身者也。自吾祖视之则鸤鸠至仁。奚有间于彼此也。推所爱亦爱之义则吾祖之所爱。而我不爱之乎。吾宗人南舍人二星仲辉。蔼然有相爱之意。而不失吾宗敦睦之风。此王诞所谓鄙宗之美者也。仲辉尝与梦赉语。叹曰吾门衰矣。今日立于朝者只八人。盖指自家及龙翼,九万,梦星,天汉,天泽,之望,梦赉也。噫荀氏八龙。不为不多。又有翱翔虎班。为 王爪牙者。亦不为不多。而仲辉犹且云然者。岂其相爱之心无穷。而出于不自满之意也邪。于家牒之末。录仲辉言。以为子孙劝。书新旧谱英毅公事迹下
谨按随会还晋。未有奔魏者。司马奔魏之说妄也。扬氏族灭。亦无扬侯者。子云扬侯之称诞也。夫以二子之该博。序其先世。宜无所不详。而犹不免后人之讥。况其下者哉。今我始祖。自汝南漂泊之说。虽无见于史者。然父子相传。久而不泯。至有文人故老记语而传说者。是以谱氏录之以示后人。但所记多有可疑者。今不得不辨。按历代沿革志。唐贞观初。始置诸使司职。有巡察安抚之号。神龙景云开元间。沿革不一。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4L 页
 而亦无按廉使。今曰仕唐为按廉使。或者以是为扬侯之称也。又按唐史明皇幸蜀。出于仓卒。未至成都。从官不满三十人。比至六军至者千三百而已。朝廷命令不能行于将士。至于皇帝泣下沾襟。奚暇遣使外夷。责其侯度也。今曰明皇在蜀时。奉使日本。或者以是为奔魏之说也。是固可疑。又按天宝十五载六月。帝出奔蜀。七月至成都。东史亦曰景德王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盖天宝十五载。即景德王十五年丙申岁也。今曰天宝十四载明皇在蜀。景德王十三年遣使朝帝何也。大抵谱氏记其传闻。恐皆附会。故其颠错谬戾有如此者。故曰言不可不慎。
而亦无按廉使。今曰仕唐为按廉使。或者以是为扬侯之称也。又按唐史明皇幸蜀。出于仓卒。未至成都。从官不满三十人。比至六军至者千三百而已。朝廷命令不能行于将士。至于皇帝泣下沾襟。奚暇遣使外夷。责其侯度也。今曰明皇在蜀时。奉使日本。或者以是为奔魏之说也。是固可疑。又按天宝十五载六月。帝出奔蜀。七月至成都。东史亦曰景德王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盖天宝十五载。即景德王十五年丙申岁也。今曰天宝十四载明皇在蜀。景德王十三年遣使朝帝何也。大抵谱氏记其传闻。恐皆附会。故其颠错谬戾有如此者。故曰言不可不慎。书英毅公以下密直公以上世系下
谨按谱氏所录世系官衔如此。既曰稽之古籍。又曰校诸碑志。谱氏之为说。亦多證左。然所谓古籍。乃洪武庚午籍。而碑志是典理府君及乐安府君墓志铭也。今按志铭帐籍。密直副使以下世系。班班可考。以上则无可凭者。谱氏何以的密直为之卓之子而不以为疑乎。说者谓古谱然也。然今考南奕世系。古谱则系于星老之下。帐籍则系于之卓之下。然则古谱亦何可尽信也。且始祖四代孙洪辅称以重大匡会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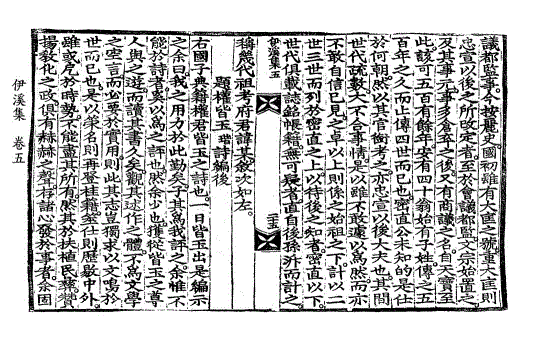 议都监事。今按丽史。国初虽有大匡之号。重大匡则忠宣以后之所改定者。至于会议都监。文宗始置之。及其事元。事多仓卒之后。又有商议之名。自天宝至此。该可五百有馀年。安有四十翁始有子姓。传之五百年之久而止传四世而已也。密直公未知的是仕于何朝。然以其官衔考之。亦忠宣以后大夫也。其间世代疏数。大不合事情。是以虽不敢遽以为然。而亦不敢自信己见。之卓以上则系之始祖之下。计以二世三世而列于密直之上。以待后之知者。密直以下。世代俱载志铭帐籍。无可疑者。直自后孙溯而计之。称几代祖考府君讳某。叙次如左。
议都监事。今按丽史。国初虽有大匡之号。重大匡则忠宣以后之所改定者。至于会议都监。文宗始置之。及其事元。事多仓卒之后。又有商议之名。自天宝至此。该可五百有馀年。安有四十翁始有子姓。传之五百年之久而止传四世而已也。密直公未知的是仕于何朝。然以其官衔考之。亦忠宣以后大夫也。其间世代疏数。大不合事情。是以虽不敢遽以为然。而亦不敢自信己见。之卓以上则系之始祖之下。计以二世三世而列于密直之上。以待后之知者。密直以下。世代俱载志铭帐籍。无可疑者。直自后孙溯而计之。称几代祖考府君讳某。叙次如左。题权皆玉(瑎)诗编后
右国子典籍权君皆玉之诗也。一日皆玉出是编示之余曰。我之用力于此勤矣。子其为我评之。余惟不能于诗者。奚以为之评也。然余少也。获从皆玉之尊人与之游。而读其书久矣。观其述作之体。不为文学之空言。而必要于实用。则此其志岂独求以文鸣于世而已也。是以策名则再登桂籍。筮仕则历扬中外。虽或厄于时势。不能尽其所有。然其于扶植民彝。赞扬教化之政。俱有赫赫之声。存诸心发于事者。余固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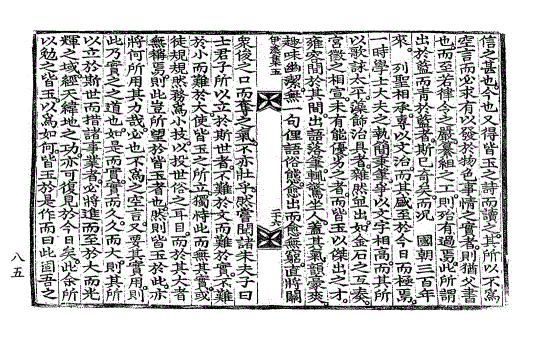 信之甚也。今也又得皆玉之诗而读之。其所以不为空言而必求有以发于物色事情之实者。则犹父书也。而至若律令之严。纂组之工。则殆有过焉。此所谓出于蓝而青于蓝者。斯已奇矣。而况 国朝三百年来。 列圣相承。专以文治。而其盛至于今日而极焉。一时学士大夫之执简秉笔。争以文字相高。而其所以歌咏太平。藻饰治具者。杂然并出。如金石之互奏。宫徵之相宣。未有能优劣之者。而皆玉以杰出之才。雍容间于其间。出语落笔。辄惊坐人。盖其气韵豪爽。趣味幽洁。无一句俚语俗态。愈出而愈无穷。直将关众俊之口而夺之气。不亦壮乎。然尝闻诸朱夫子曰士君子所以立于斯世者。不难于文而难于实。不难于小而难于大。使皆玉之所立。独恃此而无其实。或徒规规然务为小技。以投世俗之耳目。而于其大者无称焉。则此岂所望于皆玉者也。然则皆玉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也不为之空言。又要其实用。则此乃实之之道也。如是而实。实而久。久而大。则其所以立于斯世而措诸事业者。必将进而至于大而光辉之域。经天纬地之功。亦可复见于今日矣。此余所以勉之皆玉。以为如何。皆玉于是作而曰此固吾之
信之甚也。今也又得皆玉之诗而读之。其所以不为空言而必求有以发于物色事情之实者。则犹父书也。而至若律令之严。纂组之工。则殆有过焉。此所谓出于蓝而青于蓝者。斯已奇矣。而况 国朝三百年来。 列圣相承。专以文治。而其盛至于今日而极焉。一时学士大夫之执简秉笔。争以文字相高。而其所以歌咏太平。藻饰治具者。杂然并出。如金石之互奏。宫徵之相宣。未有能优劣之者。而皆玉以杰出之才。雍容间于其间。出语落笔。辄惊坐人。盖其气韵豪爽。趣味幽洁。无一句俚语俗态。愈出而愈无穷。直将关众俊之口而夺之气。不亦壮乎。然尝闻诸朱夫子曰士君子所以立于斯世者。不难于文而难于实。不难于小而难于大。使皆玉之所立。独恃此而无其实。或徒规规然务为小技。以投世俗之耳目。而于其大者无称焉。则此岂所望于皆玉者也。然则皆玉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也不为之空言。又要其实用。则此乃实之之道也。如是而实。实而久。久而大。则其所以立于斯世而措诸事业者。必将进而至于大而光辉之域。经天纬地之功。亦可复见于今日矣。此余所以勉之皆玉。以为如何。皆玉于是作而曰此固吾之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6H 页
 所愿学而病未能者。请书而记诸卷末。庶乎有以自砺也。余不获让。因书其说而归之。
所愿学而病未能者。请书而记诸卷末。庶乎有以自砺也。余不获让。因书其说而归之。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铭
石鼎铭
尔性顽吾亦顽。尔形孱吾亦孱。饘于粥于。朝耳暮耳。不愿人之膏粱兮。吾与尔兮相终始。
三寅剑铭
百神观。三寅成。猗欤剑。秋水寒。隙月明。猗欤剑。红霓泣。白帝惊。猗欤剑。匣中藏。以时鸣。猗欤剑。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笺
冬至贺笺
紫极天临。方切华封之祝。玄机阳复。伫看泰运之亨。半夜鸣雷。万物涵泽。恭惟功参位育。德合生成。玉烛调元。不愆迭运。行之时序。璿玑齐政。允协无改移之天心。玆当闭关之辰。益迓锡民之庆。伏念臣惭非地望。叨守雷封。迹滞南州。丹衷随一线之日。心悬 北阙。白首瞻五色之云。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上梁文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6L 页
 鸣鹤书院上梁文(院在任实九皋县。享己卯名贤。含城朴先生薰,修心斋朴先生蕃。盖二先生从父兄弟也。)
鸣鹤书院上梁文(院在任实九皋县。享己卯名贤。含城朴先生薰,修心斋朴先生蕃。盖二先生从父兄弟也。)先贤设教于人。既垂启佑之范。后学宜祭于社。敢稽崇报之仪。忽见栋宇之翚飞。争腾远近之燕贺。粤我云水之县。介在完带之间。由来百年。素多孝弟之士。虽曰十室。岂无忠信之人。恭惟含城朴先生。孝性出天。实见得地。左右就养。既见野鸭之飞来。甘旨何常。亦有山獐之自至。恭为子职。可作百世之师。不匮孝思。奚但一时之誉。暨我修心斋朴先生。气禀清淑。性惟端良。学而知闻而知。追武步于阃域。生以礼死以礼。尽终始于庭闱。草木始蕃之时。能守无咎之义。箪瓢屡空之日。益确不改之操。惟玆两贤之生。咸萃一家之内。胡门之明仲仁仲。岂有造诣之浅深。东方之大连少连。亦无时世之先后。五世之遗泽不斩。一方之公论未湮。命旌门闾。夫非 圣君之宠。祠欠血食。实是吾党之羞。如余鲁莽小儒。幸忝邹邑太守。山斗瞻仰。几切景慕之诚。井里徘徊。殆同私淑之地。爰考白鹿洞旧制。仍拓鸣鹤亭新基。兴感之俊彦同声。经营筹度。召募之工徒殚力。役事奔趋。矩斯方规斯圆。绳墨不差其分。大为杗小为桷。长短各适其宜。不失兄弟之连床。亦在菟裘之古里。明灵庶几来格。陟降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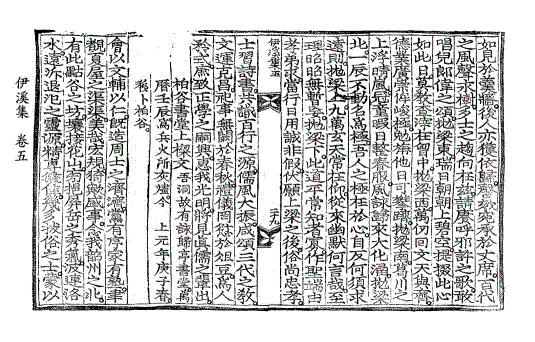 如见于羹墙。后人亦获依归。謦欬宛承于丈席。百代之风声永树。多士之趋向在玆。请赓呼邪许之歌。敢唱儿郎伟之颂。抛梁东。瑞日朝朝上碧空。提掇此心如此日。莫教查滓在胸中。抛梁西。万仞回文天与齐。德业广崇侔峻极。勉旃他日可攀跻。抛梁南。葛川之上浮晴岚。冠童暇日整春服。风咏归来大化涵。抛梁北。一辰不动名为极。吾人之极在于心。自反何须求远则。抛梁上。九万玄天常在仰。从来幽默何言哉。至理昭昭无暂妄。抛梁下。此道平常知者寡。作圣端由孝弟求。当行日用诚非假。伏愿上梁之后。俗尚忠孝。士习诗书。共识百行之源。儒风大振。咸颂三代之教。文运克昌。祀事无阙于春秋。礼仪罔愆于俎豆。为人矜式。庶致正学之嗣兴。惠我光明。将见真儒之辈出。
如见于羹墙。后人亦获依归。謦欬宛承于丈席。百代之风声永树。多士之趋向在玆。请赓呼邪许之歌。敢唱儿郎伟之颂。抛梁东。瑞日朝朝上碧空。提掇此心如此日。莫教查滓在胸中。抛梁西。万仞回文天与齐。德业广崇侔峻极。勉旃他日可攀跻。抛梁南。葛川之上浮晴岚。冠童暇日整春服。风咏归来大化涵。抛梁北。一辰不动名为极。吾人之极在于心。自反何须求远则。抛梁上。九万玄天常在仰。从来幽默何言哉。至理昭昭无暂妄。抛梁下。此道平常知者寡。作圣端由孝弟求。当行日用诚非假。伏愿上梁之后。俗尚忠孝。士习诗书。共识百行之源。儒风大振。咸颂三代之教。文运克昌。祀事无阙于春秋。礼仪罔愆于俎豆。为人矜式。庶致正学之嗣兴。惠我光明。将见真儒之辈出。柏谷书堂上梁文(吾洞故有咏归亭书堂。万历壬辰。为兵火所灰烬。今 上元年庚子春。移卜柏谷。)
会以文辅以仁。既造周士之济济。党有序家有塾。聿睹夏屋之渠渠。美哉宏规。猗欤盛事。念我韶州之北。有此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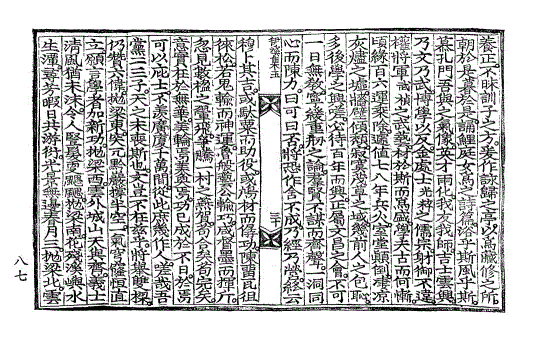 养正。不昧训子之方。爰作咏归之亭。以为藏修之所。朝于是暮于是。诵鲤庭女为之诗篇。浴乎斯风乎斯。慕孔门吾与之气像。英才雨化。我友我师。吉士云兴。乃文乃武。博学以反。金处士(光粹)之儒宗。射御不违。权将军(武桢)之武艺。材于斯而为盛。学夫古而何惭。顷缘百六运乘除。遽值七八年兵火。室堂颠倒。凄凉灰烬之墟。墙壁倾颓。寂寞茂草之域。几前人之包耻。多后学之兴嗟。必待百年而兴。正属文昌之会。不可一日无教。宁缓重刱之论。群贤不谋而齐声。一洞同心而陈力。曰可曰否。将恐作舍不成。乃经乃营。终云穆卜其吉。或驮粟而助役。或鸠材而僝功。陈留瓦徂徕松。若鬼输而神运。鲁般艺公输巧。咸督墨而挥斤。忽见数楹之翚飞。争腾一村之燕贺。苟合矣苟完矣。意实在于无华。美轮焉美奂焉。功已成于不日。于焉可以庇士。不羡广厦千万间。从此庶几作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天之未丧斯也。文岂不在玆乎。将举双梁。仍赞六伟。抛梁东。突兀黔岩撑半空。一气穹窿恒直立。愿言学者加新功。抛梁西。云外城山天与齐。义士清风犹未沫。令人竖发更飔飔。抛梁南。花残溪屿水生潭。寻芳暇日共游衍。光景无边春月三。抛梁北。云
养正。不昧训子之方。爰作咏归之亭。以为藏修之所。朝于是暮于是。诵鲤庭女为之诗篇。浴乎斯风乎斯。慕孔门吾与之气像。英才雨化。我友我师。吉士云兴。乃文乃武。博学以反。金处士(光粹)之儒宗。射御不违。权将军(武桢)之武艺。材于斯而为盛。学夫古而何惭。顷缘百六运乘除。遽值七八年兵火。室堂颠倒。凄凉灰烬之墟。墙壁倾颓。寂寞茂草之域。几前人之包耻。多后学之兴嗟。必待百年而兴。正属文昌之会。不可一日无教。宁缓重刱之论。群贤不谋而齐声。一洞同心而陈力。曰可曰否。将恐作舍不成。乃经乃营。终云穆卜其吉。或驮粟而助役。或鸠材而僝功。陈留瓦徂徕松。若鬼输而神运。鲁般艺公输巧。咸督墨而挥斤。忽见数楹之翚飞。争腾一村之燕贺。苟合矣苟完矣。意实在于无华。美轮焉美奂焉。功已成于不日。于焉可以庇士。不羡广厦千万间。从此庶几作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天之未丧斯也。文岂不在玆乎。将举双梁。仍赞六伟。抛梁东。突兀黔岩撑半空。一气穹窿恒直立。愿言学者加新功。抛梁西。云外城山天与齐。义士清风犹未沫。令人竖发更飔飔。抛梁南。花残溪屿水生潭。寻芳暇日共游衍。光景无边春月三。抛梁北。云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8H 页
 寺禅钟声在即。恍若同安县里闻。不妨因此求心学。抛梁上。至健天行垂太象。一理昭昭寓不言。玄苍幽默真无妄。抛梁下。以顺承天惟地也。有美无成万化光。人臣道有同然者。伏愿上梁之后。家弦户诵。春乐冬书。德相劝礼相交。不失蓝田之约。入则孝出则弟。一变邹鲁之风。书堂化玉堂。将见 王猷之黼黻。小学入大学。岂独公车之计偕。文起八代衰微。化及三韩黎庶。
寺禅钟声在即。恍若同安县里闻。不妨因此求心学。抛梁上。至健天行垂太象。一理昭昭寓不言。玄苍幽默真无妄。抛梁下。以顺承天惟地也。有美无成万化光。人臣道有同然者。伏愿上梁之后。家弦户诵。春乐冬书。德相劝礼相交。不失蓝田之约。入则孝出则弟。一变邹鲁之风。书堂化玉堂。将见 王猷之黼黻。小学入大学。岂独公车之计偕。文起八代衰微。化及三韩黎庶。新宁乡校圣殿上梁文
道未尝亡也。允协革旧之人心。文不在玆乎。聿睹鼎新之庙貌。杏坛生色。槐市增辉。窃念东方学校之大兴。盖自我 朝祖宗而尤盛。州有三百六十。孰非夫子之宫。人无贵贱贤愚。尽是尊亲之士。不可一日无者。所以三代共之。今玆丁火之乡。古者辰韩之域。废为银户。曾世代之悠悠。徙居花山。而众庶之皞皞。人人慕忠孝。一变昔金之遗风。家家诵诗书。非复甄丽之故俗。莫非素王之化。敢忘崇象之方。惟思式礼之罔愆。于乐閟宫之有侐。我将我享。左右之群贤洋洋。来燕来宁。前后之元哲揭揭。横经问难之语。恍若同时。盛服齐明之风。将期来世。流诵声于璧水。煽文化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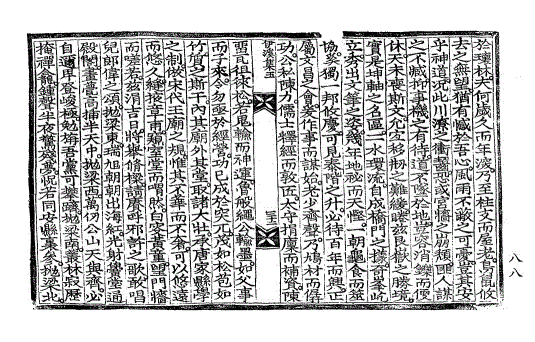 于瑰林。夫何岁久而年深。乃至柱支而屋老。鸟鼠攸去之无望。犹有憾于吾心。风雨不蔽之可忧。岂其安乎神道。况此川潦之冲齧。恐或宫墙之崩颓。匪人谋之不臧。抑事机之有待。道不坠于地。岂容消铄而便休。天未丧斯文。允宜移刱之难缓。眷玆艮岳之胜境。实是坤轴之名区。二水环流。自成桥门之㨾。奇峰屹立。秀出文笔之姿。几年地秘而天悭。一朝龟食而筮协。奚独一邦攸庆。可见泰阶之升。必待百年而兴。正属文昌之会。爰作事而谋始。老少齐声。乃鸠材而僝功。公私陈力。儒士释经而敦匠。太守捐廪而补资。陈留瓦徂徕松。若鬼输而神运。鲁般绳公输墨。如父事而子来。令勿亟于经营。功已成于突兀。茂如松苞如竹。质之斯干。内其庙外其堂。取诸大壮。承唐家县学之制。仿宋代王庙之规。惟其不华而不奢。可以悠远而悠久。缝掖章甫。窥室堂而喟然。白叟黄童。望门墙而嗟若。玆涓吉日。将举脩梁。请赓呼邪许之歌。敢唱儿郎伟之颂。抛梁东。瑞旭朝朝出海红。光射黉堂通殿阁。画甍高插半天中。抛梁西。万仞公山天与齐。必自迩卑登峻极。勉旃吾党可攀跻。抛梁南。丛林寂历掩禅龛。钟声半夜惊残梦。恍若同安县里参。抛梁北。
于瑰林。夫何岁久而年深。乃至柱支而屋老。鸟鼠攸去之无望。犹有憾于吾心。风雨不蔽之可忧。岂其安乎神道。况此川潦之冲齧。恐或宫墙之崩颓。匪人谋之不臧。抑事机之有待。道不坠于地。岂容消铄而便休。天未丧斯文。允宜移刱之难缓。眷玆艮岳之胜境。实是坤轴之名区。二水环流。自成桥门之㨾。奇峰屹立。秀出文笔之姿。几年地秘而天悭。一朝龟食而筮协。奚独一邦攸庆。可见泰阶之升。必待百年而兴。正属文昌之会。爰作事而谋始。老少齐声。乃鸠材而僝功。公私陈力。儒士释经而敦匠。太守捐廪而补资。陈留瓦徂徕松。若鬼输而神运。鲁般绳公输墨。如父事而子来。令勿亟于经营。功已成于突兀。茂如松苞如竹。质之斯干。内其庙外其堂。取诸大壮。承唐家县学之制。仿宋代王庙之规。惟其不华而不奢。可以悠远而悠久。缝掖章甫。窥室堂而喟然。白叟黄童。望门墙而嗟若。玆涓吉日。将举脩梁。请赓呼邪许之歌。敢唱儿郎伟之颂。抛梁东。瑞旭朝朝出海红。光射黉堂通殿阁。画甍高插半天中。抛梁西。万仞公山天与齐。必自迩卑登峻极。勉旃吾党可攀跻。抛梁南。丛林寂历掩禅龛。钟声半夜惊残梦。恍若同安县里参。抛梁北。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9H 页
 众星错落拱宸极。为君臣者定于斯。圣训明明在方策。抛梁上。昆仑漠漠垂玄象。从来幽默何言哉。生物行时无暂妄。抛梁下。混混源泉流不舍。亚圣一言岂我欺。盈科而进如斯也。伏愿上梁之后。家弦户诵。秋礼冬诗。尚入孝出弟之风。奋希贤慕圣之志。人皆忠信。释老杨墨之说不行。学必明诚。孔颜思孟之道益著。风俗变化。多俊髦于一方。天地氤氲。启文教于百代。
众星错落拱宸极。为君臣者定于斯。圣训明明在方策。抛梁上。昆仑漠漠垂玄象。从来幽默何言哉。生物行时无暂妄。抛梁下。混混源泉流不舍。亚圣一言岂我欺。盈科而进如斯也。伏愿上梁之后。家弦户诵。秋礼冬诗。尚入孝出弟之风。奋希贤慕圣之志。人皆忠信。释老杨墨之说不行。学必明诚。孔颜思孟之道益著。风俗变化。多俊髦于一方。天地氤氲。启文教于百代。元兴洞旧书院庙上梁文
崇厥德不掩尔善。既有秉彝之天。祭于社其在斯人。可无妥灵之地。有侐数间之庙宇。聿新四方之瞻聆。粤自徐罗旧邦。有此义城新府。二水分流于前后。会于洛江朝于九溟。诸山环镇乎东西。起为金城结为五土。扶舆灵淑之气。亭育豪杰之才。当丽祖创业之时。有洪术洪儒之武。逮 圣朝兴平之日。称金淳金末之文。言功名而固难胜枚。语真儒则请姑舍是。伏惟松隐金先生。情高意逸。行安学成。用而行舍而藏。浮云富贵。入则孝出则弟。馀事文章。警心十章箴。盖有得于三纲领八条目。丰城一片剑。亦何害于二鸟赋九辩歌。作模楷于当时。树风声于来世。如今百年
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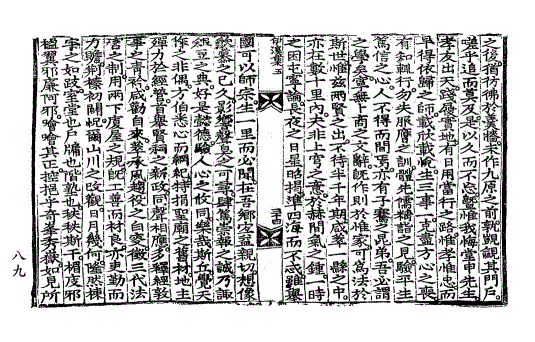 之后。犹彷佛于羹墙。未作九原之前。孰觊觎其门户。嗟乎追而莫及。是以久而不忘。暨惟我悔堂申先生。孝友出天。践履实地。有日用当行之路。惟孝惟忠。而早得依归之师。载欣载悦。生三事一。克尽方心之丧。有知辄行。勿失服膺之训。体先儒精诣之见。验平生笃信之心。人不得而间焉。亦有子骞之昆弟。吾必谓之学矣。宁无卜商之文辞。既作则于惟家。可为法于斯世。惟玆两贤之出。不待半千年期。咸萃一县之中。亦在数十里内。夫非上穹之意。于赫间气之钟。一时之困屯宁论。长夜之日星昭揭。准四海而不忒。虽举国可以师宗。生一里而必闻。在吾乡宜益亲切。想像欣慕之已久。影响声臭之可寻。肆笃崇报之诚。乃诹俎豆之典。好是懿德。验人心之攸同。乐哉斯丘。觉天作之非偶。方伯悉心而纲纪。特捐圣庙之旧材。地主殚力于经营。首举贤祠之新政。同声相应。多释经敦事之青衿。咸劝自来。萃承风趋役之白叟。徵三代法宫之制。用两下厦屋之规。既工善而材良。亦吏勤而力赡。荆榛初辟。恍尔山川之改观。日月几何。隆然栋宇之如跂。室堂也户牖也阶塾也。秩秩斯干。楣庋邪楹翼邪廉阿邪。哙哙其正。控挹乎奇峰秀岳。如见所
之后。犹彷佛于羹墙。未作九原之前。孰觊觎其门户。嗟乎追而莫及。是以久而不忘。暨惟我悔堂申先生。孝友出天。践履实地。有日用当行之路。惟孝惟忠。而早得依归之师。载欣载悦。生三事一。克尽方心之丧。有知辄行。勿失服膺之训。体先儒精诣之见。验平生笃信之心。人不得而间焉。亦有子骞之昆弟。吾必谓之学矣。宁无卜商之文辞。既作则于惟家。可为法于斯世。惟玆两贤之出。不待半千年期。咸萃一县之中。亦在数十里内。夫非上穹之意。于赫间气之钟。一时之困屯宁论。长夜之日星昭揭。准四海而不忒。虽举国可以师宗。生一里而必闻。在吾乡宜益亲切。想像欣慕之已久。影响声臭之可寻。肆笃崇报之诚。乃诹俎豆之典。好是懿德。验人心之攸同。乐哉斯丘。觉天作之非偶。方伯悉心而纲纪。特捐圣庙之旧材。地主殚力于经营。首举贤祠之新政。同声相应。多释经敦事之青衿。咸劝自来。萃承风趋役之白叟。徵三代法宫之制。用两下厦屋之规。既工善而材良。亦吏勤而力赡。荆榛初辟。恍尔山川之改观。日月几何。隆然栋宇之如跂。室堂也户牖也阶塾也。秩秩斯干。楣庋邪楹翼邪廉阿邪。哙哙其正。控挹乎奇峰秀岳。如见所伊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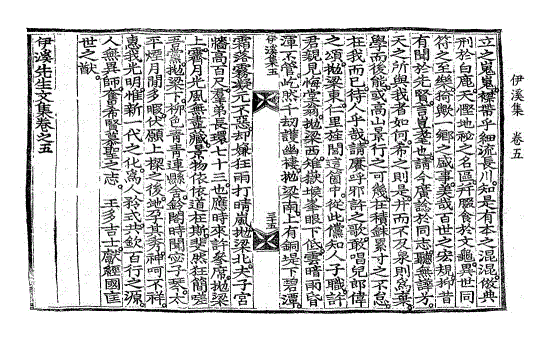 立之嵬嵬。襟带乎细流长川。知是有本之混混。仿典刑于白鹿。天悭地秘之名区。并啜食于文龟。异世同符之至乐。猗欤一乡之盛事。美哉百世之宏规。抑昔有闻于先贤。言岂耄也。请今广谂于同志。听无哗兮。天之所与我者如何。希之则是。井而不及泉则为弃。学而后能。或高山景行之可几。在积铢累寸之不怠。在我而已。待人乎哉。请赓呼邪许之歌。敢唱儿郎伟之颂。抛梁东。仁里旌闾这个中。从此傥知人子职。许君亲见悔堂翁。抛梁西。雉岳堠峰眼下低。云暗雨昏浑不管。屹然千劫护幽栖。抛梁南。上有铜堤下碧潭。霜落雾凝元不恶。却嫌狂雨打晴岚。抛梁北。夫子宫墙高百尺。群弟长环七十三。也应时来许参席。抛梁上。霁月光风无尽藏。景物依依道在斯。斐然狂简嗟吾党。抛梁下。柳色青青连县舍。铃阁时闻宓子琴。太平烟月閒多暇。伏愿上梁之后。地孕其秀。神呵不祥。惠我光明。惟新一代之化。为人矜式。共钦百行之源。人无异师。奋希贤慕圣之志。 王多吉士。献经国匡世之猷。
立之嵬嵬。襟带乎细流长川。知是有本之混混。仿典刑于白鹿。天悭地秘之名区。并啜食于文龟。异世同符之至乐。猗欤一乡之盛事。美哉百世之宏规。抑昔有闻于先贤。言岂耄也。请今广谂于同志。听无哗兮。天之所与我者如何。希之则是。井而不及泉则为弃。学而后能。或高山景行之可几。在积铢累寸之不怠。在我而已。待人乎哉。请赓呼邪许之歌。敢唱儿郎伟之颂。抛梁东。仁里旌闾这个中。从此傥知人子职。许君亲见悔堂翁。抛梁西。雉岳堠峰眼下低。云暗雨昏浑不管。屹然千劫护幽栖。抛梁南。上有铜堤下碧潭。霜落雾凝元不恶。却嫌狂雨打晴岚。抛梁北。夫子宫墙高百尺。群弟长环七十三。也应时来许参席。抛梁上。霁月光风无尽藏。景物依依道在斯。斐然狂简嗟吾党。抛梁下。柳色青青连县舍。铃阁时闻宓子琴。太平烟月閒多暇。伏愿上梁之后。地孕其秀。神呵不祥。惠我光明。惟新一代之化。为人矜式。共钦百行之源。人无异师。奋希贤慕圣之志。 王多吉士。献经国匡世之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