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x 页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赋
赋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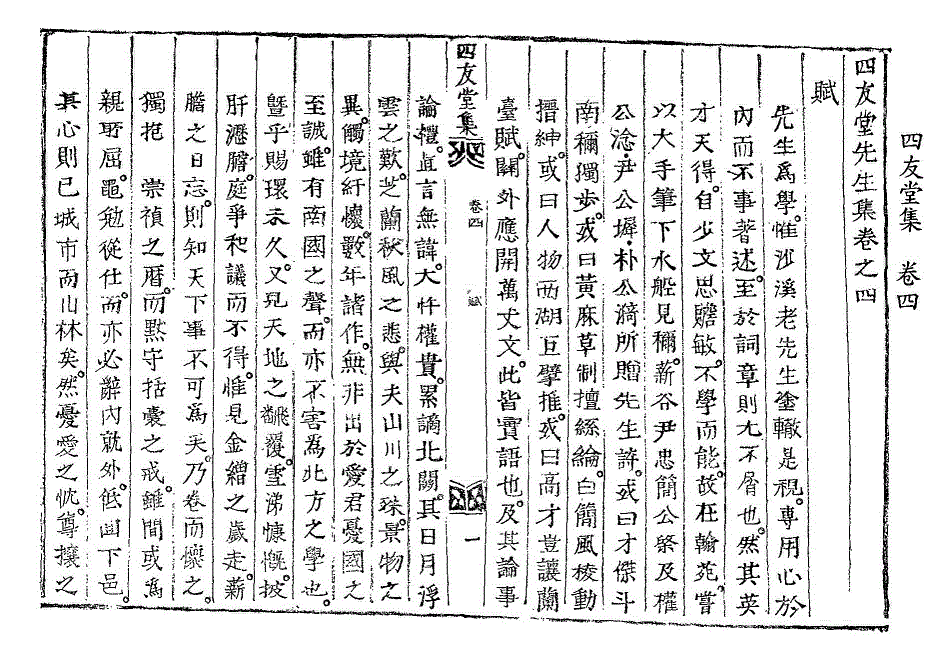 (附)识[黄以章]
(附)识[黄以章]先生为学。惟沙溪老先生涂辙是视。专用心于内而不事著述。至于词章则尤不屑也。然其英才天得。自少文思赡敏。不学而能。故在翰苑。尝以大手笔下水船见称。薪谷尹忠简公棨及权公淰,尹公墀,朴公漪所赠先生诗。或曰才杰斗南称独步。或曰黄麻草制擅丝纶。白简风棱动搢绅。或曰人物西湖巨擘推。或曰高才岂让兰台赋。关外应开万丈文。此皆实语也。及其论事论礼。直言无讳。大忤权贵。累谪北关。其日月浮云之叹。芝兰秋风之悲。与夫山川之殊。景物之异。触境纡怀。数年诸作。无非出于爱君忧国之至诚。虽有南国之声。而亦不害为北方之学也。暨乎赐环未久。又见天地之翻覆。雪涕慷慨。披肝沥胆。庭争和议而不得。惟见金缯之岁走。薪胆之日忘。则知天下事不可为矣。乃卷而怀之。独抱 崇祯之历。而默守括囊之戒。虽间或为亲所屈。黾勉从仕。而亦必辞内就外。低回下邑。其心则已城市而山林矣。然忧爱之忱。尊攘之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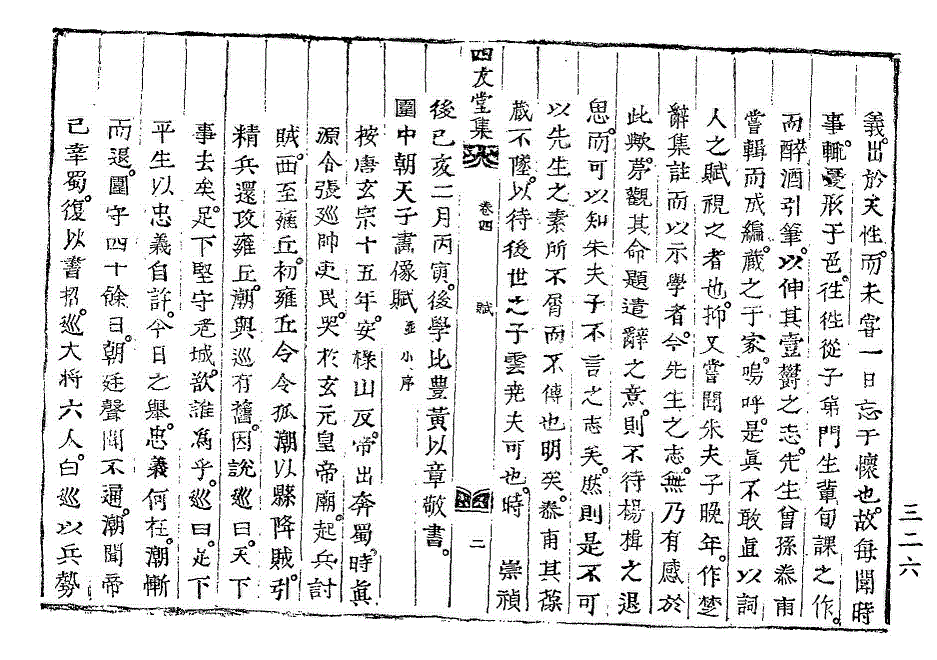 义。出于天性。而未尝一日忘于怀也。故每闻时事。辄忧形于色。往往从子弟门生辈旬课之作。而醉酒引笔。以伸其壹郁之志。先生曾孙泰甫尝辑而成编。藏之于家。呜呼。是真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者也。抑又尝闻朱夫子晚年。作楚辞集注而以示学者。今先生之志。无乃有感于此欤。第观其命题遣辞之意。则不待杨楫之退思。而可以知朱夫子不言之志矣。然则是不可以先生之素所不屑而不传也明矣。泰甫其葆藏不坠。以待后世之子云尧夫可也。时 崇祯后己亥二月丙寅。后学比礼黄以章敬书。
义。出于天性。而未尝一日忘于怀也。故每闻时事。辄忧形于色。往往从子弟门生辈旬课之作。而醉酒引笔。以伸其壹郁之志。先生曾孙泰甫尝辑而成编。藏之于家。呜呼。是真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者也。抑又尝闻朱夫子晚年。作楚辞集注而以示学者。今先生之志。无乃有感于此欤。第观其命题遣辞之意。则不待杨楫之退思。而可以知朱夫子不言之志矣。然则是不可以先生之素所不屑而不传也明矣。泰甫其葆藏不坠。以待后世之子云尧夫可也。时 崇祯后己亥二月丙寅。后学比礼黄以章敬书。围中朝天子画像赋(并小序)
按唐玄宗十五年。安禄山反。帝出奔蜀。时真源令张巡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西至雍丘。初雍丘令令狐潮以县降贼。引精兵还攻雍丘。潮与巡有旧。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围守四十馀日。朝廷声闻不通。潮闻帝已幸蜀。复以书招。巡大将六人。白巡以兵势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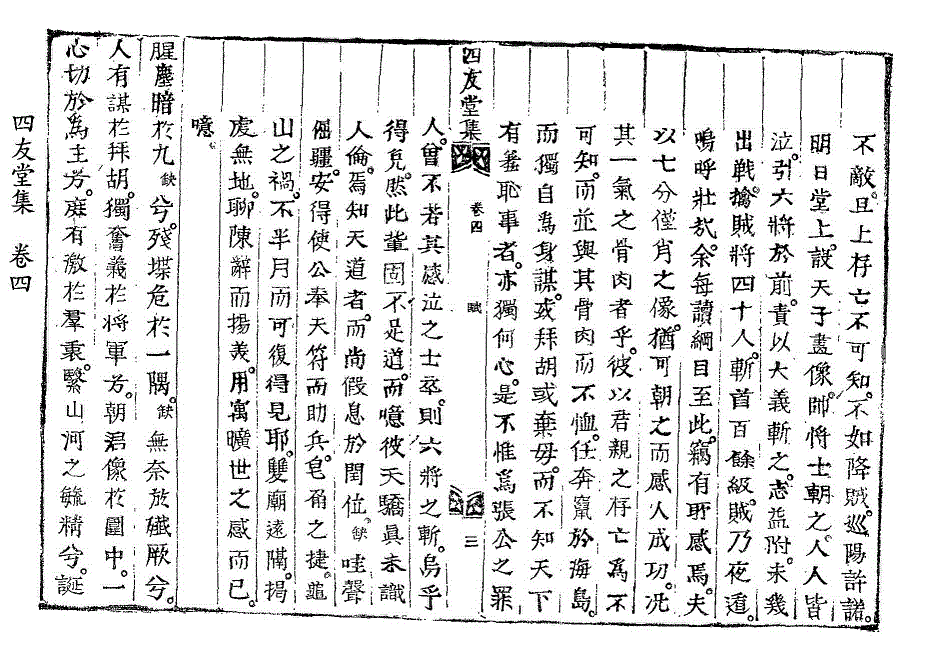 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志益附。未几出战。擒贼将四十人。斩首百馀级。贼乃夜遁。呜呼壮哉。余每读纲目至此。窃有所感焉。夫以七分仅肖之像。犹可朝之而感人成功。况其一气之骨肉者乎。彼以君亲之存亡为不可知。而并与其骨肉而不恤。任奔窜于海岛。而独自为身谋。或拜胡或弃母。而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者。亦独何心。是不惟为张公之罪人。曾不若其感泣之士卒。则六将之斩。乌乎得免。然此辈固不足道。而噫彼天骄真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者。而尚假息于闰位。(缺)哇声倔疆。安得使公奉天符而助兵。皂角之捷。龟山之祸。不半月而可复得见耶。双庙远隔。揭虔无地。聊陈辞而扬美。用寓旷世之感而已。噫。
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志益附。未几出战。擒贼将四十人。斩首百馀级。贼乃夜遁。呜呼壮哉。余每读纲目至此。窃有所感焉。夫以七分仅肖之像。犹可朝之而感人成功。况其一气之骨肉者乎。彼以君亲之存亡为不可知。而并与其骨肉而不恤。任奔窜于海岛。而独自为身谋。或拜胡或弃母。而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者。亦独何心。是不惟为张公之罪人。曾不若其感泣之士卒。则六将之斩。乌乎得免。然此辈固不足道。而噫彼天骄真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者。而尚假息于闰位。(缺)哇声倔疆。安得使公奉天符而助兵。皂角之捷。龟山之祸。不半月而可复得见耶。双庙远隔。揭虔无地。聊陈辞而扬美。用寓旷世之感而已。噫。腥尘暗于九(缺)兮。残堞危于一隅。(缺)无奈于歼厥兮。人有谋于拜胡。独奋义于将军兮。朝君像于围中。一心切于为主兮。庶有激于群衷。繄山河之毓精兮。诞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7L 页
 一介之张公。手三尺之青萍兮。心一斗之丹衷。分铜虎于百里兮。任保障于一域。志既笃于殉国兮。义存亡于休戚。时长鲸之猾夏兮。动𥀷鼓于渔阳。惊风雨于半夜兮。矢忽及于黄屋。输金瓯于羯奴兮。播玉辇于鸟栈。悯生灵之涂炭兮。痛王业之累卵。有血气者咸愤兮。矧我公之忠烈。哭一声于古庙兮。人数千之同心。将天讨之大义兮。誓旧物之匡复。迨功业之未半兮。城忽危于三匝。顾所操之弥坚兮。义敢忘于君臣。何褊裨之不忠兮。有反侧之阴谋。纷争趍于卖降兮。大事去于朝暮。愤已激于孤忠兮。顾何术以厉众。运奇智于方寸兮。像至尊于一幅。俨置诸于堂上兮。宛彩眉于半壁。率群下而载朝兮。勤拜手而稽首。天颜近于尺五兮。谅吾君之在玆。岂人心之无憾兮。泫将士之涕泣。鼓义气于一军兮。诛已加于六将。士回心于死长兮。功忽收于一战。非精忠之贯日兮。讵所为之若是。当危堞之月翚兮。势方急于三坂。人争谋于降贼兮。公独有此抗义。既感人于事一兮。又明罪于怀二。谅临危而善处兮。尽忠心之攸发。沿千载而想像兮。能使人而竖发。何忠愤之未泄兮。奄壮图之夭阏。色不变于当刃兮。果前后之一节。呜呼北风兮
一介之张公。手三尺之青萍兮。心一斗之丹衷。分铜虎于百里兮。任保障于一域。志既笃于殉国兮。义存亡于休戚。时长鲸之猾夏兮。动𥀷鼓于渔阳。惊风雨于半夜兮。矢忽及于黄屋。输金瓯于羯奴兮。播玉辇于鸟栈。悯生灵之涂炭兮。痛王业之累卵。有血气者咸愤兮。矧我公之忠烈。哭一声于古庙兮。人数千之同心。将天讨之大义兮。誓旧物之匡复。迨功业之未半兮。城忽危于三匝。顾所操之弥坚兮。义敢忘于君臣。何褊裨之不忠兮。有反侧之阴谋。纷争趍于卖降兮。大事去于朝暮。愤已激于孤忠兮。顾何术以厉众。运奇智于方寸兮。像至尊于一幅。俨置诸于堂上兮。宛彩眉于半壁。率群下而载朝兮。勤拜手而稽首。天颜近于尺五兮。谅吾君之在玆。岂人心之无憾兮。泫将士之涕泣。鼓义气于一军兮。诛已加于六将。士回心于死长兮。功忽收于一战。非精忠之贯日兮。讵所为之若是。当危堞之月翚兮。势方急于三坂。人争谋于降贼兮。公独有此抗义。既感人于事一兮。又明罪于怀二。谅临危而善处兮。尽忠心之攸发。沿千载而想像兮。能使人而竖发。何忠愤之未泄兮。奄壮图之夭阏。色不变于当刃兮。果前后之一节。呜呼北风兮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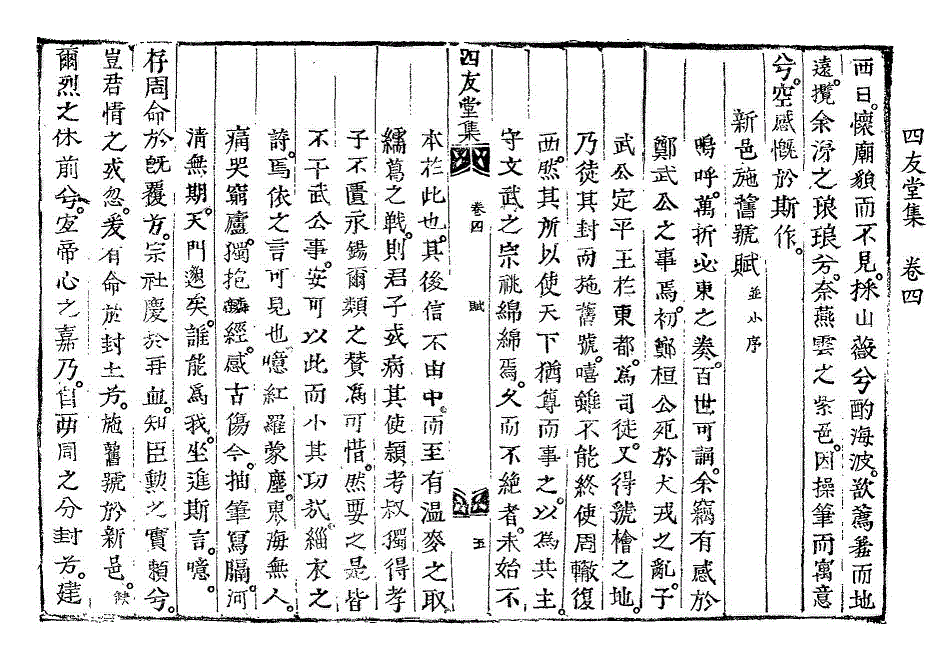 西日。怀庙貌而不见。采山薇兮酌海波。欲荐羞而地远。揽余涕之琅琅兮。奈燕云之紫色。因操笔而寓意兮。空感慨于斯作。
西日。怀庙貌而不见。采山薇兮酌海波。欲荐羞而地远。揽余涕之琅琅兮。奈燕云之紫色。因操笔而寓意兮。空感慨于斯作。新邑施旧号赋(并小序)
呜呼。万折必东之奏。百世可诵。余窃有感于郑武公之事焉。初郑桓公死于犬戎之乱。子武公定平王于东都。为司徒。又得虢桧之地。乃徒其封而施旧号。嘻虽不能终使周辙复西。然其所以使天下犹尊而事之。以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绵绵焉。久而不绝者。未始不本于此也。其后信不由中。而至有温麦之取。繻葛之战。则君子或病其使颖考叔独得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赞为可惜。然要之是皆不干武公事。安可以此而小其功哉。缁衣之诗。焉依之言可见也。噫红罗蒙尘。东海无人。痛哭穷庐。独抱麟经。感古伤今。抽笔写膈。河清无期。天门邈矣。谁能为我。坐进斯言。噫。
存周命于既覆兮。宗社庆于再血。知臣勋之实赖兮。岂君情之或忽。爰有命于封土兮。施旧号于新邑。(缺)尔烈之休前兮。宜帝心之嘉乃。自西周之分封兮。建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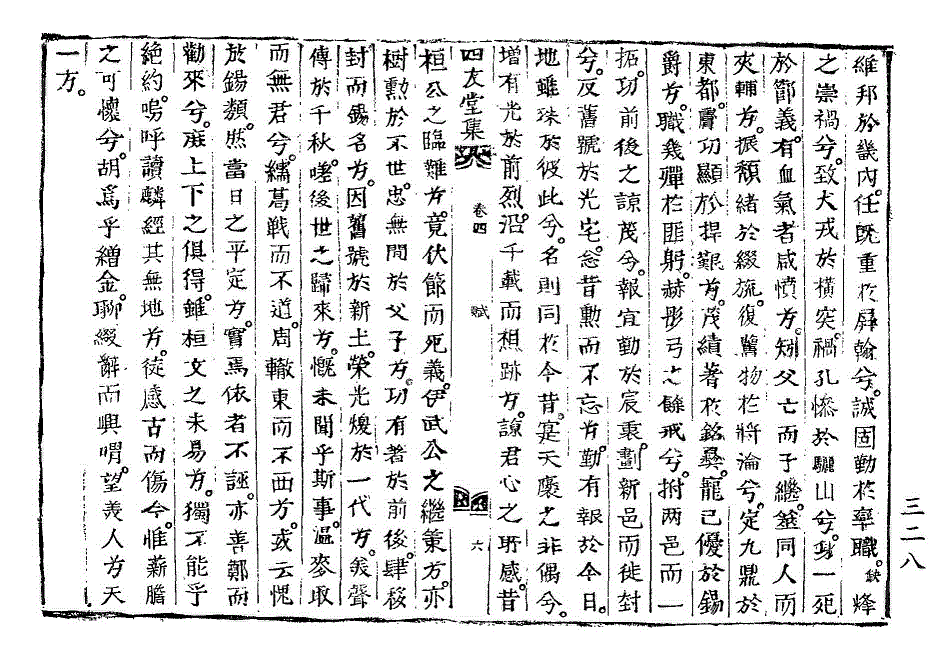 维邦于畿内。任既重于屏翰兮。诚固勤于率职。(缺)烽之崇祸兮。致犬戎于横突。祸孔惨于骊山兮。身一死于节义。有血气者咸愤兮。矧父亡而子继。筮同人而夹辅兮。振颓绪于缀旒。复旧物于将沦兮。定九鼎于东都。肤功显于捍艰兮。茂绩著于铭彝。宠已优于锡爵兮。职几殚于匪躬。赫彤弓之馀戒兮。拊两邑而一拓。功前后之谅茂兮。报宜勤于宸衷。划新邑而徙封兮。反旧号于光宅。念昔勋而不忘兮。勤有报于今日。地虽殊于彼此兮。名则同于今昔。寔天褒之非偶兮。增有光于前烈。沿千载而想迹兮。谅君心之所感。昔桓公之临难兮。竟伏节而死义。伊武公之继策兮。亦树勋于不世。忠无间于父子兮。功有著于前后。肆移封而锡名兮。因旧号于新土。荣光焕于一代兮。美声传于千秋。嗟后世之归来兮。慨未闻乎斯事。温麦取而无君兮。繻葛战而不道。周辙东而不西兮。或云愧于锡类。然当日之平定兮。实焉依者不诬。亦善郑而劝来兮。庶上下之俱得。虽桓文之未易兮。独不能乎绝约。呜呼读麟经其无地兮。徒感古而伤今。惟薪胆之可怀兮。胡为乎缯金。聊缀辞而兴喟。望美人兮天一方。
维邦于畿内。任既重于屏翰兮。诚固勤于率职。(缺)烽之崇祸兮。致犬戎于横突。祸孔惨于骊山兮。身一死于节义。有血气者咸愤兮。矧父亡而子继。筮同人而夹辅兮。振颓绪于缀旒。复旧物于将沦兮。定九鼎于东都。肤功显于捍艰兮。茂绩著于铭彝。宠已优于锡爵兮。职几殚于匪躬。赫彤弓之馀戒兮。拊两邑而一拓。功前后之谅茂兮。报宜勤于宸衷。划新邑而徙封兮。反旧号于光宅。念昔勋而不忘兮。勤有报于今日。地虽殊于彼此兮。名则同于今昔。寔天褒之非偶兮。增有光于前烈。沿千载而想迹兮。谅君心之所感。昔桓公之临难兮。竟伏节而死义。伊武公之继策兮。亦树勋于不世。忠无间于父子兮。功有著于前后。肆移封而锡名兮。因旧号于新土。荣光焕于一代兮。美声传于千秋。嗟后世之归来兮。慨未闻乎斯事。温麦取而无君兮。繻葛战而不道。周辙东而不西兮。或云愧于锡类。然当日之平定兮。实焉依者不诬。亦善郑而劝来兮。庶上下之俱得。虽桓文之未易兮。独不能乎绝约。呜呼读麟经其无地兮。徒感古而伤今。惟薪胆之可怀兮。胡为乎缯金。聊缀辞而兴喟。望美人兮天一方。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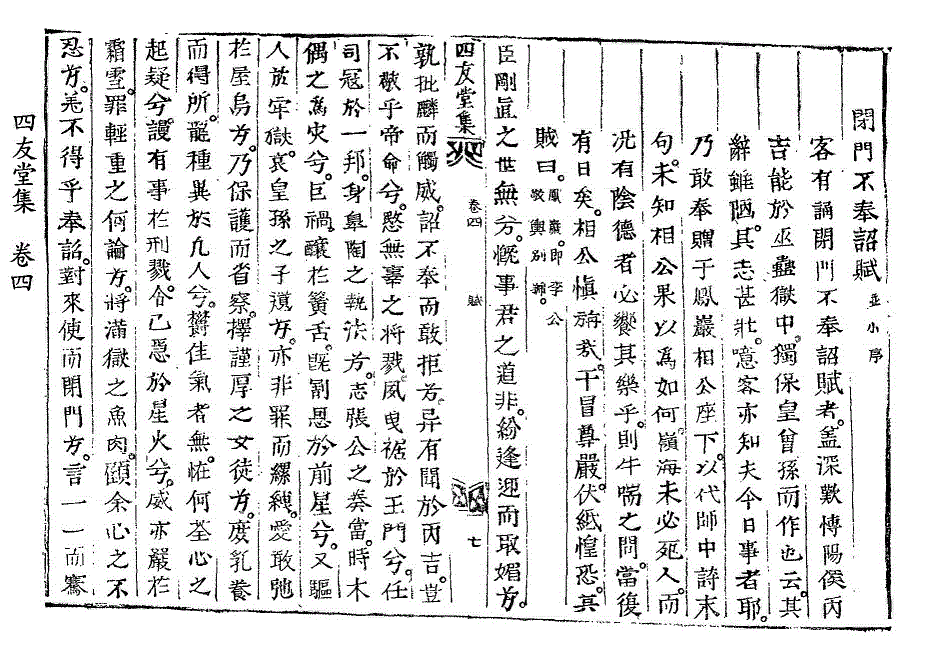 闭门不奉诏赋(并小序)
闭门不奉诏赋(并小序)客有诵闭门不奉诏赋者。盖深叹博阳侯丙吉能于巫蛊狱中。独保皇曾孙而作也云。其辞虽陋。其志甚壮。噫客亦知夫今日事者耶。乃敢奉赠于凤岩相公座下。以代师中诗末句。未知相公果以为如何。岭海未必死人。而况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乎。则牛喘之问。当复有日矣。相公慎旃哉。干冒尊严。伏纸惶恐。其贼(一作赋)曰。(凤岩。即李公敬舆别号。)
臣刚直之世无兮。慨事君之道非。纷逢迎而取媚兮。孰批麟而触威。诏不奉而敢拒兮。异有闻于丙吉。岂不敬乎帝命兮。悯无辜之将戮。夙曳裾于王门兮。任司寇于一邦。身皋陶之执法兮。志张公之奏当。时木偶之为灾兮。巨祸酿于簧舌。既割恩于前星兮。又驱人于牢狱。哀皇孙之子遗兮。亦非罪而缧绁。爱敢弛于屋乌兮。乃保护而省察。择谨厚之女徒兮。庶乳养而得所。龙种异于凡人兮。郁佳气者无怪。何荃心之起疑兮。谩有事于刑戮。令已急于星火兮。威亦严于霜雪。罪轻重之何论兮。将满狱之鱼肉。顾余心之不忍兮。羌不得乎奉诏。对来使而闭门兮。言一一而骞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29L 页
 謇。曰微臣之承命兮。纵天威之难犯。彼不辜之何杀兮。宁自失乎不经。矧储贰之遗孙兮。曾不啻乎他人。虽君命之至严兮。刑岂加于冤枉。言忠直而有义兮。果帝心之感寤。迹当日而想像兮。风可动于千秋。君有命而反拒兮。固臣子之所难。慎用刑而钦恤兮。亦前圣之所戒。伊夫公之此举兮。卓今古而罕俦。彼白头之讼冤兮。亦庶几而无及。汉宗社之复振兮。功实(缺)于夫子。竟燮理于黄扉兮。名亦焕于麒麟。玆表出而陈辞兮。作遗法于人臣。
謇。曰微臣之承命兮。纵天威之难犯。彼不辜之何杀兮。宁自失乎不经。矧储贰之遗孙兮。曾不啻乎他人。虽君命之至严兮。刑岂加于冤枉。言忠直而有义兮。果帝心之感寤。迹当日而想像兮。风可动于千秋。君有命而反拒兮。固臣子之所难。慎用刑而钦恤兮。亦前圣之所戒。伊夫公之此举兮。卓今古而罕俦。彼白头之讼冤兮。亦庶几而无及。汉宗社之复振兮。功实(缺)于夫子。竟燮理于黄扉兮。名亦焕于麒麟。玆表出而陈辞兮。作遗法于人臣。寇贾同车赋(并小序)
顾今天下事未定矣。上下殿而不失和气。虽或未易言。而寇贾之同车。是将顺光武之美也。亦不得以见之耶。漆妇苦心。夜不成寐。为赋一篇。遥寄东床。幸禀于趍庭之际。而公亦毋或为姊子之侍侧。则实世道之幸也。(东床即清风府院君金公佑明。时潜谷力主大同之议。与慎独先生不合。潜谷上疏自劾。语颇侵慎斋。慎斋遂上疏归乡。 上有廉蔺战国之士。尚能忍辱相下。以济国事之语。)
稽山泽而端蓍兮。认君子之惩忿。诛范雎之必报兮。颗廉颇之肉袒。得美事于汉纪兮。有二子之同车。解旧日之憾怨兮。共此夕之淡如。际同人之倾否兮。有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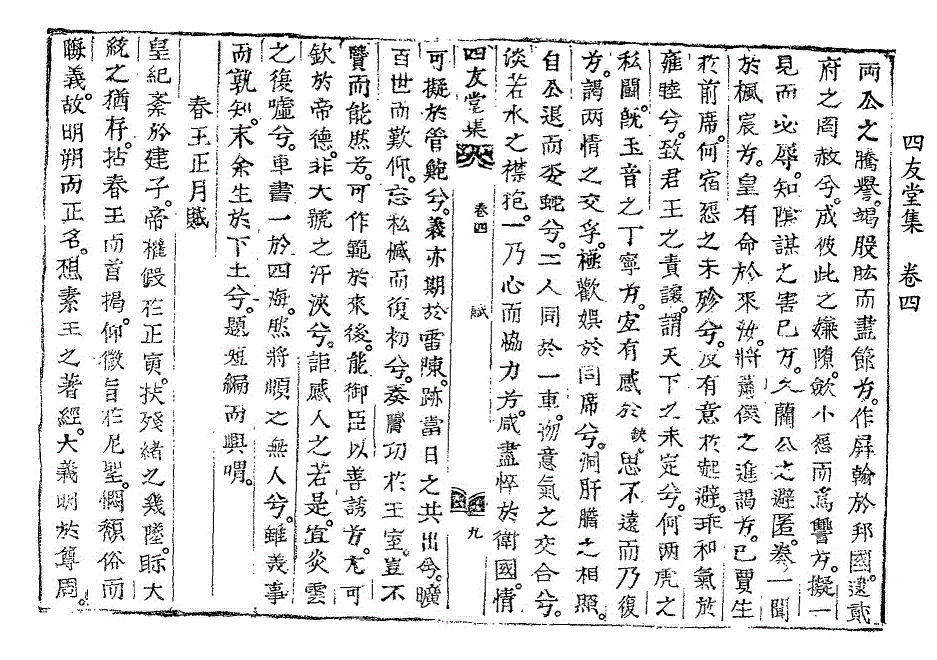 两公之腾誉。竭股肱而尽节兮。作屏翰于邦国。逮贰府之罔赦兮。成彼此之嫌隙。敛小怨而为雠兮。拟一见而必辱。知阴谋之害己兮。久蔺公之避匿。奏一闻于枫宸兮。皇有命于来汝。将萧侯之进谒兮。已贾生于前席。何宿怨之未殄兮。反有意于起避。乖和气于雍睦兮。致君王之责让。谓天下之未定兮。何两虎之私斗。既玉音之丁宁兮。宜有感于(缺)。思不远而乃复兮。谒两情之交孚。极欢娱于同席兮。洞肝胆之相照。自公退而委蛇兮。二人同于一车。沕意气之交合兮。淡若水之襟抱。一乃心而协力兮。咸尽悴于卫国。情可拟于管鲍兮。义亦期于雷陈。迹当日之共出兮。旷百世而叹仰。忘私憾而复初兮。奏肤功于王室。岂不贤而能然兮。可作范于来后。能御臣以善诱兮。尤可钦于帝德。非大号之汗浃兮。讵感人之若是。宜炎云之复嘘兮。车书一于四海。然将顺之无人兮。虽美事而孰知。末余生于下土兮。题短编而兴喟。
两公之腾誉。竭股肱而尽节兮。作屏翰于邦国。逮贰府之罔赦兮。成彼此之嫌隙。敛小怨而为雠兮。拟一见而必辱。知阴谋之害己兮。久蔺公之避匿。奏一闻于枫宸兮。皇有命于来汝。将萧侯之进谒兮。已贾生于前席。何宿怨之未殄兮。反有意于起避。乖和气于雍睦兮。致君王之责让。谓天下之未定兮。何两虎之私斗。既玉音之丁宁兮。宜有感于(缺)。思不远而乃复兮。谒两情之交孚。极欢娱于同席兮。洞肝胆之相照。自公退而委蛇兮。二人同于一车。沕意气之交合兮。淡若水之襟抱。一乃心而协力兮。咸尽悴于卫国。情可拟于管鲍兮。义亦期于雷陈。迹当日之共出兮。旷百世而叹仰。忘私憾而复初兮。奏肤功于王室。岂不贤而能然兮。可作范于来后。能御臣以善诱兮。尤可钦于帝德。非大号之汗浃兮。讵感人之若是。宜炎云之复嘘兮。车书一于四海。然将顺之无人兮。虽美事而孰知。末余生于下土兮。题短编而兴喟。春王正月赋
皇纪紊于建子。帝权假于正寅。扶残绪之几坠。视大统之犹存。拈春王而首揭。仰微旨于尼圣。悯颓俗而晦义。故明朔而正名。想素王之著经。大义明于尊周。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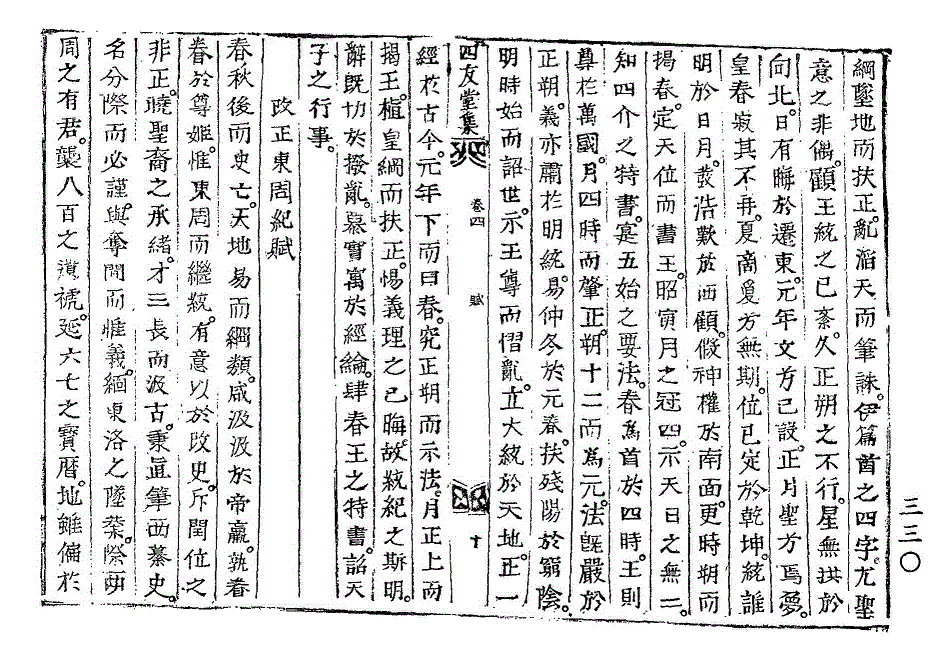 纲坠地而扶正。乱滔天而笔诛。伊篇首之四字。尤圣意之非偶。顾王统之已紊。久正朔之不行。星无拱于向北。日有晦于迁东。元年文兮已设。正月圣兮焉梦。皇春寂其不再。夏商夐兮无期。位已定于乾坤。统谁明于日月。发浩叹于西顾。假神权于南面。更时朔而揭春。定天位而书王。昭寅月之冠四。示天日之无二。知四介之特书。寔五始之要法。春为首于四时。王则尊于万国。月四时而肇正。朔十二而为元。法既严于正朔。义亦肃于明统。易仲冬于元春。扶残阳于穷阴。明时始而诏世。示王尊而慑乱。立大统于天地。正一经于古今。元年下而曰春。究正朔而示法。月正上而揭王。植皇纲而扶正。惕义理之已晦。故统纪之斯明。辞既切于拨乱。慕实寓于经纶。肆春王之特书。诏天子之行事。
纲坠地而扶正。乱滔天而笔诛。伊篇首之四字。尤圣意之非偶。顾王统之已紊。久正朔之不行。星无拱于向北。日有晦于迁东。元年文兮已设。正月圣兮焉梦。皇春寂其不再。夏商夐兮无期。位已定于乾坤。统谁明于日月。发浩叹于西顾。假神权于南面。更时朔而揭春。定天位而书王。昭寅月之冠四。示天日之无二。知四介之特书。寔五始之要法。春为首于四时。王则尊于万国。月四时而肇正。朔十二而为元。法既严于正朔。义亦肃于明统。易仲冬于元春。扶残阳于穷阴。明时始而诏世。示王尊而慑乱。立大统于天地。正一经于古今。元年下而曰春。究正朔而示法。月正上而揭王。植皇纲而扶正。惕义理之已晦。故统纪之斯明。辞既切于拨乱。慕实寓于经纶。肆春王之特书。诏天子之行事。改正东周纪赋
春秋后而史亡。天地易而綗类。咸汲汲于帝羸。孰眷眷于尊姬。惟东周而继统。有意以于改史。斥闰位之非正。晓圣裔之承绪。才三长而汲古。秉直笔西纂史。名分际而必谨。与夺间而惟义。缅东洛之坠业。际西周之有君。袭八百之遗褫。延六七之宝历。地虽偏于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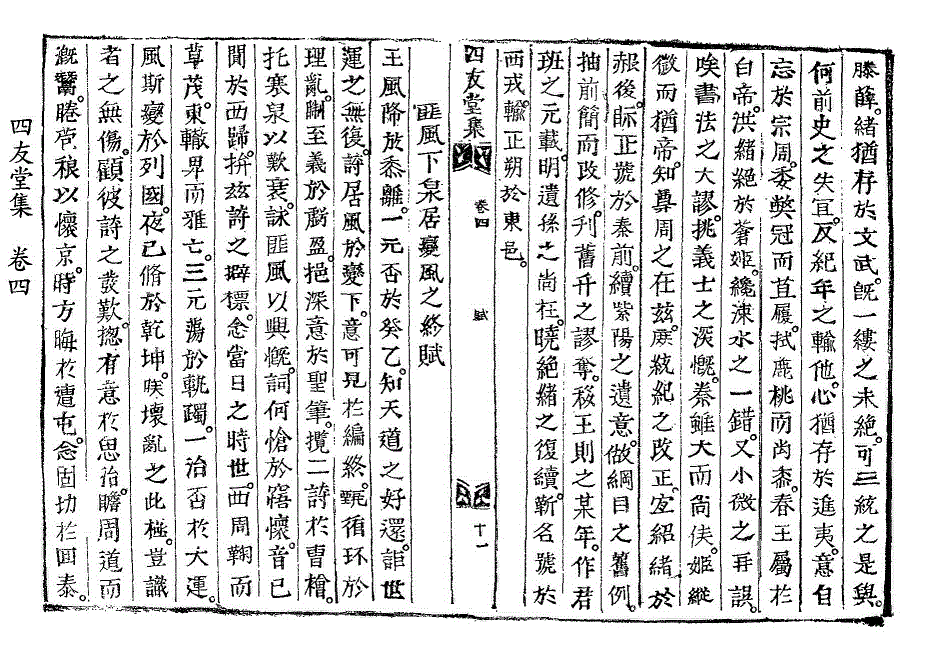 滕薛。绪犹存于文武。既一缕之未绝。可三统之是与。何前史之失宜。反纪年之输他。心犹存于进夷。意自忘于宗周。委弊冠而苴履。拭粗桃而尚黍。春王属于白帝。洪绪绝于苍姬。才涑水之一错。又小微之再误。唉书法之大谬。挑义士之深慨。秦虽大而尚侯。姬纵微而犹帝。知尊周之在玆。庶统纪之改正。宜绍绪于赧后。视正号于秦前。续紫阳之遗意。做纲目之旧例。抽前简而改修。刊旧竹之谬夺。移王则之某年。作君班之元载。明遗孙之尚在。晓绝绪之复续。靳名号于西戎。输正朔于东邑。
滕薛。绪犹存于文武。既一缕之未绝。可三统之是与。何前史之失宜。反纪年之输他。心犹存于进夷。意自忘于宗周。委弊冠而苴履。拭粗桃而尚黍。春王属于白帝。洪绪绝于苍姬。才涑水之一错。又小微之再误。唉书法之大谬。挑义士之深慨。秦虽大而尚侯。姬纵微而犹帝。知尊周之在玆。庶统纪之改正。宜绍绪于赧后。视正号于秦前。续紫阳之遗意。做纲目之旧例。抽前简而改修。刊旧竹之谬夺。移王则之某年。作君班之元载。明遗孙之尚在。晓绝绪之复续。靳名号于西戎。输正朔于东邑。匪风下泉居变风之终赋
王风降于黍离。一元否于癸乙。知天道之好还。讵世运之无复。诗居风于变下。意可见于编终。甄循环于理乱。晢至义于亏盈。挹深意于圣笔。揽二诗于曹桧。托寒泉以叹衰。咏匪风以兴慨。词何怆于寤怀。音已阒于西归。拚玆诗之擗标。念当日之时世。西周鞠而草茂。东辙卑而雅亡。三元荡于轨躅。一治否于大运。风斯变于列国。夜已脩于乾坤。唉坏乱之此极。岂识者之无伤。顾彼诗之发叹。揔有意于思治。瞻周道而溉鬵。眷苞稂以怀京。时方晦于遭屯。念固切于回泰。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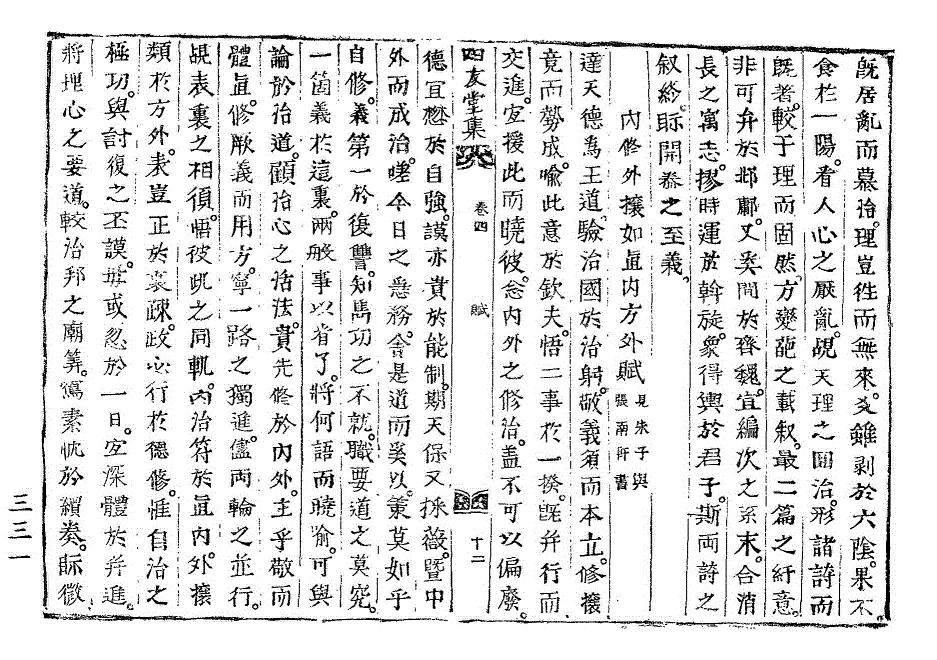 既居乱而慕治。理岂往而无来。爻虽剥于六阴。果不食于一阳。看人心之厌乱。觇天理之回治。形诸诗而既著。较于理而固然。方变葩之载叙。最二篇之纡意。非可弁于邶鄘。又奚间于齐魏。宜编次之系末。合消长之寓志。摎时运于斡旋。象得舆于君子。斯两诗之叙终。视开泰之至义。
既居乱而慕治。理岂往而无来。爻虽剥于六阴。果不食于一阳。看人心之厌乱。觇天理之回治。形诸诗而既著。较于理而固然。方变葩之载叙。最二篇之纡意。非可弁于邶鄘。又奚间于齐魏。宜编次之系末。合消长之寓志。摎时运于斡旋。象得舆于君子。斯两诗之叙终。视开泰之至义。内修外攘如直内方外赋(见朱子与张南轩书)
达天德为王道。验治国于治躬。敬义须而本立。修攘竟而势成。喻此意于钦夫。悟二事于一揆。既并行而交进。宜援此而晓彼。念内外之修治。盖不可以偏废。德宜懋于自强。谟亦贵于能制。期天保又采薇。暨中外而成治。嗟今日之急务。舍是道而奚以。策莫如乎自修。义第一于复雠。知隽功之不就。职要道之莫究。一个义于这里。两般事以看了。将何语而晓喻。可与论于治道。顾治心之活法。贵先修于内外。主乎敬而体直。修厥义而用方。宁一路之独进。尽两轮之并行。觇表里之相须。悟彼此之同轨。内治符于直内。外攘类于方外。表岂正于里疏。政必行于德修。惟自治之极功。与讨复之丕谟。毋或忽于一日。宜深体于并进。将理心之要道。较治邦之庙算。写素忱于续奏。视微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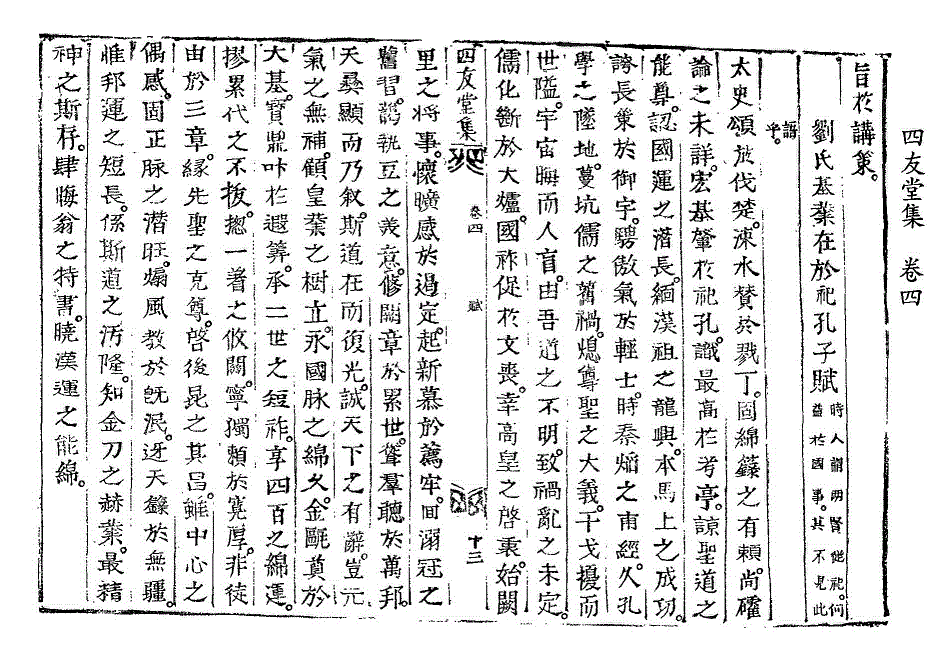 旨于讲策。
旨于讲策。刘氏基业在于祀孔子赋(时人谓两贤从祀。何益于国事。其不见此语乎。)
太史颂于伐楚。涑水赞于戮丁。固绵箓之有赖。尚礭论之未详。宏基肇于祀孔。识最高于考亭。谅圣道之能尊。认国运之潜长。缅汉祖之龙兴。本马上之成功。誇长策于御宇。骋傲气于轻士。时秦焰之甫经。久孔学之坠地。蔓坑儒之旧祸。熄尊圣之大义。干戈扰而世隘。宇宙晦而人盲。由吾道之不明。致祸乱之未定。儒化断于大炉。国祚促于文丧。幸高皇之启衷。始阙里之将事。怀旷感于遏定。起新慕于荐牢。回溺冠之旧习。蔼执豆之美意。修阙章于累世。耸群听于万邦。天彝显而乃叙。斯道在而复光。诚天下之有辞。岂元气之无补。顾皇业之树立。永国脉之绵久。金瓯奠于大基。宝鼎叶于遐算。承二世之短祚。享四百之绵运。摎累代之不拔。揔一着之攸关。宁独赖于宽厚。非徒由于三章。缘先圣之克尊。启后昆之其昌。虽中心之偶感。固正脉之潜旺。煽风教于既泯。迓天箓于无疆。惟邦运之短长。系斯道之污隆。知金刀之赫业。最精神之斯存。肆晦翁之特书。晓汉运之能绵。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2L 页
 已觉天颜非昔时赋(出朱子戊申封事)
已觉天颜非昔时赋(出朱子戊申封事)天门瞹以岁晏。揽琼佩而愁予。秋兰猗而夕华。春树瞑于西虚。辰倏忽而不再。望日表而陈辞。挢年岁之莫与。兼进修之及时。昔疆仕余登卷。觌天颜之温粹。春容敷而始晔。庭荚莞以方茂。延和穆其日升。掔天保以遐歈。拚皇舆使整策。将导之兮天衢。佳期忽其晼晚。白露遒于杞畦。空同㵳而目眇。怅玉宸之遐阻。筼芝煌其三秀。抚桑晖而寤叹。苍颜殊于十年。瞹事君之日短。冯蒲质之已衰。悟汾飙之夕起。年洋洋而日往。混圣愚而催老。嗟少壮兮几时。恐美人之迟暮。九阍邃而重来。仰威颜于咫尺。春光晏于紫薇。华发飒于琼
传道则可。仕则不可赋。
鼎迁洛而士羞。道在我而皇求。心虽坚于罔仆。念岂忽于明彝。徵先儒之揭说。美父师之徽轨。既叙伦而甄义。认彼可而此否。天生圣而不辰。国则亡而道存。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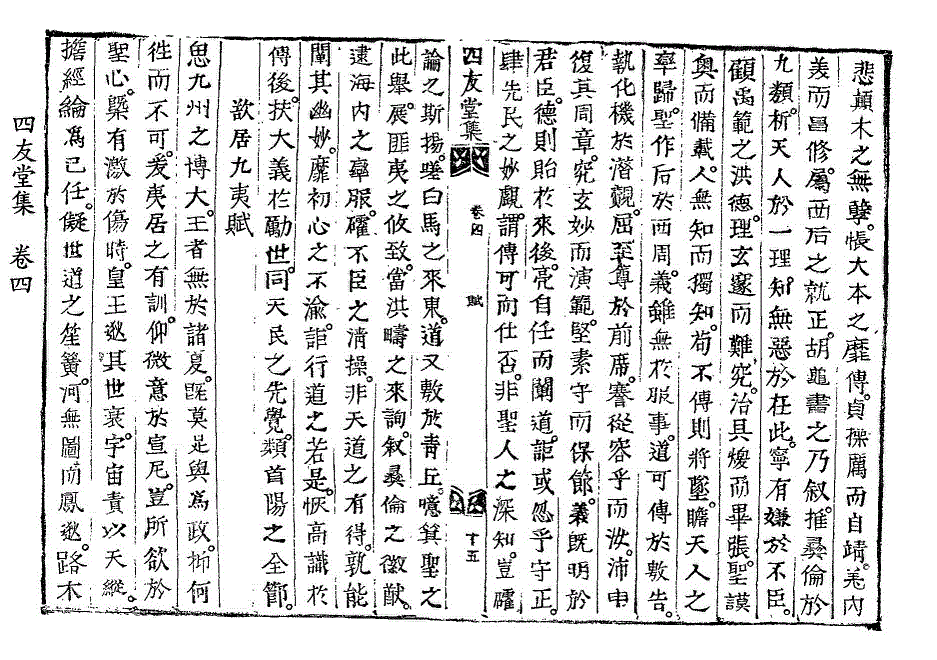 悲颠木之无孽。怅大本之靡传。贞操厉而自靖。羌内美而昌修。属西后之就正。胡龟书之乃叙。推彝伦于九类。析天人于一理。知无恶于在此。宁有嫌于不臣。顾禹范之洪德。理玄邃而难究。治具焕而毕张。圣谟奥而备载。人无知而独知。苟不传则将坠。瞻天人之率归。圣作后于西周。义虽无于服事。道可传于敷告。执化机于潜觌。屈至尊于前席。謇从容乎而汝。沛申复其周章。究玄妙而演范。坚素守而保节。义既明于君臣。德则贻于来后。亮自任而阐道。讵或忽乎守正。肆先民之妙觑。谓传可而仕否。非圣人之深知。岂礭论之斯扬。嗟白马之来东。道又敷于青丘。噫箕圣之此举。展匪夷之攸致。当洪畴之来询。叙彝伦之徽猷。逮海内之率服。礭不臣之清操。非天道之有得。孰能阐其幽妙。靡初心之不渝。讵行道之若是。恢高识于传后。扶大义于励世。同天民之先觉。类首阳之全节。
悲颠木之无孽。怅大本之靡传。贞操厉而自靖。羌内美而昌修。属西后之就正。胡龟书之乃叙。推彝伦于九类。析天人于一理。知无恶于在此。宁有嫌于不臣。顾禹范之洪德。理玄邃而难究。治具焕而毕张。圣谟奥而备载。人无知而独知。苟不传则将坠。瞻天人之率归。圣作后于西周。义虽无于服事。道可传于敷告。执化机于潜觌。屈至尊于前席。謇从容乎而汝。沛申复其周章。究玄妙而演范。坚素守而保节。义既明于君臣。德则贻于来后。亮自任而阐道。讵或忽乎守正。肆先民之妙觑。谓传可而仕否。非圣人之深知。岂礭论之斯扬。嗟白马之来东。道又敷于青丘。噫箕圣之此举。展匪夷之攸致。当洪畴之来询。叙彝伦之徽猷。逮海内之率服。礭不臣之清操。非天道之有得。孰能阐其幽妙。靡初心之不渝。讵行道之若是。恢高识于传后。扶大义于励世。同天民之先觉。类首阳之全节。欲居九夷赋
思九州之博大。王者无于诸夏。既莫足与为政。抑何往而不可。爰夷居之有训。仰微意于宣尼。岂所欲于圣心。槩有激于伤时。皇王逖其世衰。宇宙责以天纵。担经纶为己任。儗世道之笙簧。河无图而凤逖。路木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3L 页
 铎而栖遑。纷违齐而屈宋。谩泥蔡而辞吴。西方杳以苓蓁。列国昏以风雨。君惟庸而不用。道谁需而弘济。志既违于西周。叹自深于桴海。戚游辙之靡骋。瞻四方而兴言。中州隘而莫容。吾道时而能权。知蛮貊犹可行。顾何处而非民。念九夷之殊种。天以东而遐域。区玄黄而介处。语侏俪而卉服。虽无关于禹甸。幸不远于箕封。民何鄙于羯𦎗。天亦均于禀赋。苟忠信而笃敬。庶过化而存神。风吾治而草偃。夏可用而夷变。亦足进于中国。君子居之何陋。歧西生而丕显。海东治而仁贤。俗与化而易移。今不异于古云。玆吾所以欲居。谁曰夷而未可。非华土之偏狭。岂颓俗之为美。心既切于慨世。志自急于行道。岂迟迟于去故。实耿耿于居彼。
铎而栖遑。纷违齐而屈宋。谩泥蔡而辞吴。西方杳以苓蓁。列国昏以风雨。君惟庸而不用。道谁需而弘济。志既违于西周。叹自深于桴海。戚游辙之靡骋。瞻四方而兴言。中州隘而莫容。吾道时而能权。知蛮貊犹可行。顾何处而非民。念九夷之殊种。天以东而遐域。区玄黄而介处。语侏俪而卉服。虽无关于禹甸。幸不远于箕封。民何鄙于羯𦎗。天亦均于禀赋。苟忠信而笃敬。庶过化而存神。风吾治而草偃。夏可用而夷变。亦足进于中国。君子居之何陋。歧西生而丕显。海东治而仁贤。俗与化而易移。今不异于古云。玆吾所以欲居。谁曰夷而未可。非华土之偏狭。岂颓俗之为美。心既切于慨世。志自急于行道。岂迟迟于去故。实耿耿于居彼。五柳春风自一家赋
结草庐于柴桑。(缺)菊史于日月。超寄奴之世界。宛典午之风物。微风暖而柳依。自在家而高葆。节既励于耻新。境惟全于依旧。山家淡于柳下。晋士居而易安。沧桑换于故都。松菊托于幽贞。登东皋而叙啸。眄南国而何等。书车散于寰宇。版籍输于金刀。山河羞于举目。非旧物于晋家。咨四海之尽刘。畴一丘之独保。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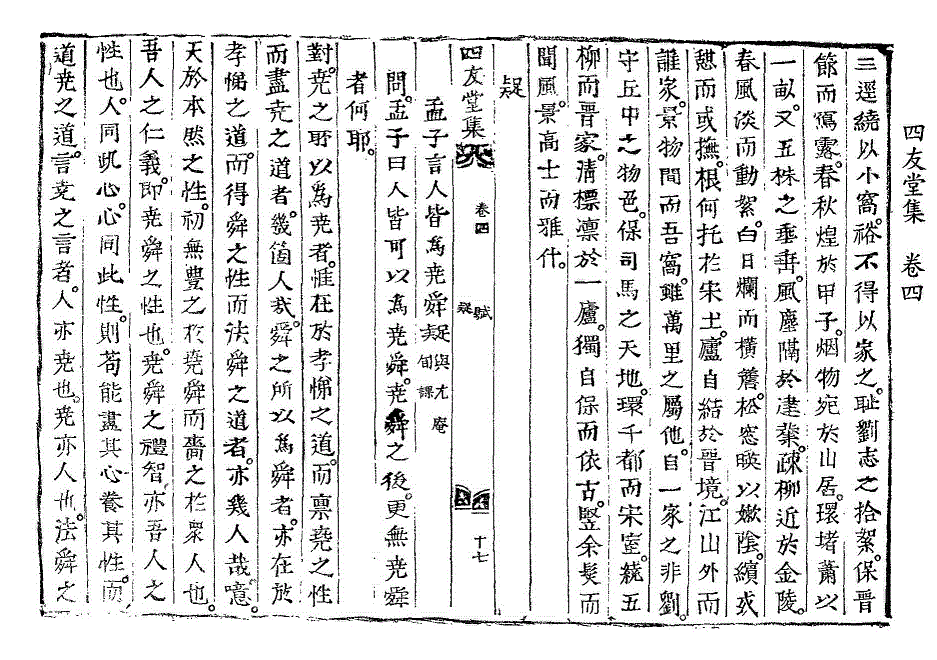 三径绕以小窝。裕不得以家之。耻刘志之拾絮。保晋节而写露。春秋煌于甲子。烟物宛于山居。环堵萧以一亩。又五株之垂垂。风尘隔于建业。疏柳近于金陵。春风淡而动絮。白日烂而横檐。松窗映以嫩阴。缤或憩而或抚。根何托于宋土。庐自结于晋境。江山外而谁家。景物间而吾窝。虽万里之属他。自一家之非刘。守丘中之物色。保司马之天地。环千都而宋室。绕五柳而晋家。清标凛于一庐。独自保而依古。竖余发而闻风。景高士而雅什。
三径绕以小窝。裕不得以家之。耻刘志之拾絮。保晋节而写露。春秋煌于甲子。烟物宛于山居。环堵萧以一亩。又五株之垂垂。风尘隔于建业。疏柳近于金陵。春风淡而动絮。白日烂而横檐。松窗映以嫩阴。缤或憩而或抚。根何托于宋土。庐自结于晋境。江山外而谁家。景物间而吾窝。虽万里之属他。自一家之非刘。守丘中之物色。保司马之天地。环千都而宋室。绕五柳而晋家。清标凛于一庐。独自保而依古。竖余发而闻风。景高士而雅什。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疑
孟子言人皆为尧舜疑(与尤庵旬课)
问。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后。更无尧舜者何耶。
对。尧之所以为尧者。惟在于孝悌之道。而禀尧之性而尽尧之道者。几个人哉。舜之所以为舜者。亦在于孝悌之道。而得舜之性而法舜之道者。亦几人哉。噫。天于本然之性。初无礼之于尧舜而啬之于众人也。吾人之仁义。即尧舜之性也。尧舜之礼智。亦吾人之性也。人同此心。心同此性。则苟能尽其心养其性。而道尧之道。言尧之言者。人亦尧也。尧亦人也。法舜之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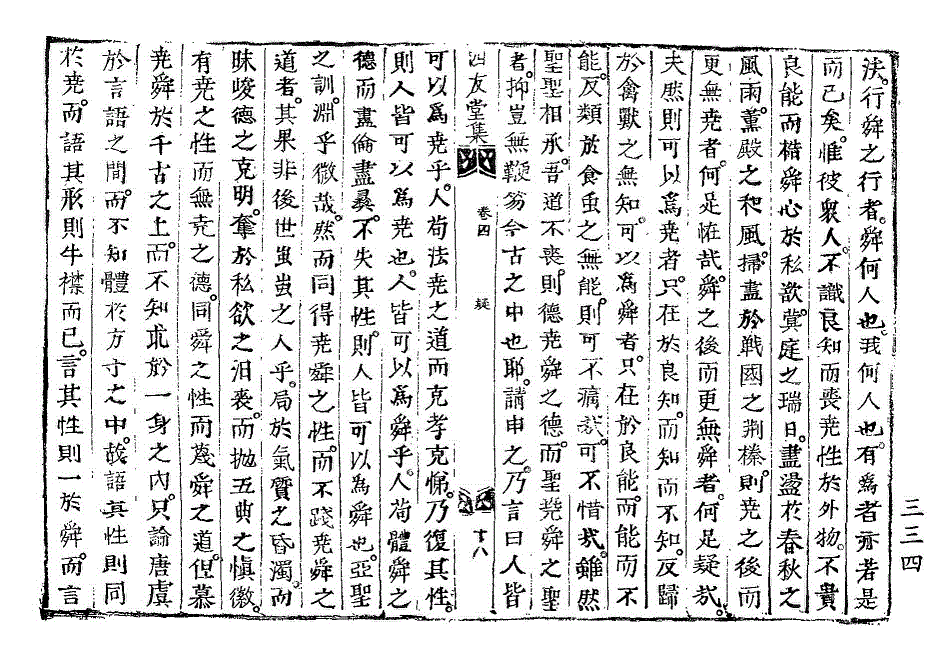 法。行舜之行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已矣。惟彼众人。不识良知而丧尧性于外物。不贵良能而梏舜心于私欲。蓂庭之瑞日。尽荡于春秋之风雨。薰殿之和风。扫尽于战国之荆榛。则尧之后而更无尧者。何足怪哉。舜之后而更无舜者。何足疑哉。夫然则可以为尧者。只在于良知。而知而不知。反归于禽兽之无知。可以为舜者。只在于良能。而能而不能。反类于食虫之无能。则可不痛哉。可不惜哉。虽然圣圣相承。吾道不丧。则德尧舜之德。而圣尧舜之圣者。抑岂无鞭笏今古之中也耶。请申之。乃言曰人皆可以为尧乎。人苟法尧之道而克孝克悌。乃复其性。则人皆可以为尧也。人皆可以为舜乎。人苟体舜之德而尽伦尽彝。不失其性。则人皆可以为舜也。亚圣之训。渊乎微哉。然而同得尧舜之性。而不践尧舜之道者。其果非后世蚩蚩之人乎。局于气质之昏浊。而昧峻德之克明。夺于私欲之汩丧。而抛五典之慎徽。有尧之性而无尧之德。同舜之性而蔑舜之道。但慕尧舜于千古之上。而不知求于一身之内。只论唐虞于言语之间。而不知体于方寸之中。故语其性则同于尧。而语其形则牛襟而已。言其性则一于舜。而言
法。行舜之行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已矣。惟彼众人。不识良知而丧尧性于外物。不贵良能而梏舜心于私欲。蓂庭之瑞日。尽荡于春秋之风雨。薰殿之和风。扫尽于战国之荆榛。则尧之后而更无尧者。何足怪哉。舜之后而更无舜者。何足疑哉。夫然则可以为尧者。只在于良知。而知而不知。反归于禽兽之无知。可以为舜者。只在于良能。而能而不能。反类于食虫之无能。则可不痛哉。可不惜哉。虽然圣圣相承。吾道不丧。则德尧舜之德。而圣尧舜之圣者。抑岂无鞭笏今古之中也耶。请申之。乃言曰人皆可以为尧乎。人苟法尧之道而克孝克悌。乃复其性。则人皆可以为尧也。人皆可以为舜乎。人苟体舜之德而尽伦尽彝。不失其性。则人皆可以为舜也。亚圣之训。渊乎微哉。然而同得尧舜之性。而不践尧舜之道者。其果非后世蚩蚩之人乎。局于气质之昏浊。而昧峻德之克明。夺于私欲之汩丧。而抛五典之慎徽。有尧之性而无尧之德。同舜之性而蔑舜之道。但慕尧舜于千古之上。而不知求于一身之内。只论唐虞于言语之间。而不知体于方寸之中。故语其性则同于尧。而语其形则牛襟而已。言其性则一于舜。而言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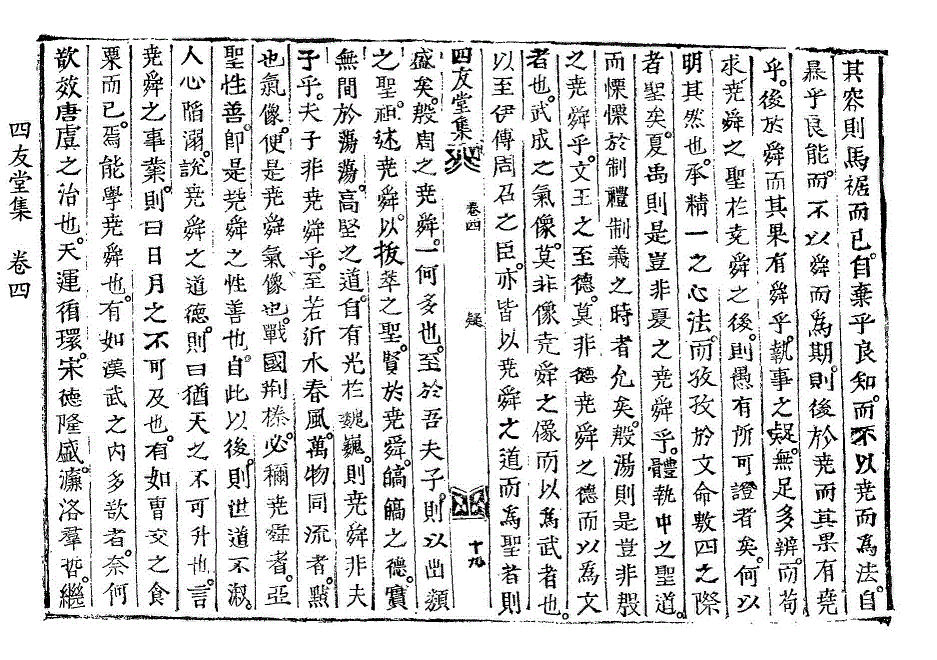 其容则马裾而已。自弃乎良知。而不以尧而为法。自暴乎良能。而不以舜而为期。则后于尧而其果有尧乎。后于舜而其果有舜乎。执事之疑。无足多辨。而苟求尧舜之圣于尧舜之后。则愚有所可證者矣。何以明其然也。承精一之心法。而孜孜于文命敷四之际者圣矣。夏禹则是岂非夏之尧舜乎。体执中之圣道。而慄慄于制礼制义之时者允矣。殷汤则是岂非殷之尧舜乎。文王之至德。莫非德尧舜之德而以为文者也。武成之气像。莫非像尧舜之像而以为武者也。以至伊傅周召之臣。亦皆以尧舜之道而为圣者则盛矣。殷周之尧舜。一何多也。至于吾夫子。则以出类之圣。祖述尧舜。以拔萃之圣。贤于尧舜。皓皓之德。实无间于荡荡。高坚之道。自有光于魏巍。则尧舜非夫子乎。夫子非尧舜乎。至若沂水春风。万物同流者。点也气像。便是尧舜气像也。战国荆榛。必称尧舜者。亚圣性善。即是尧舜之性善也。自此以后。则世道不淑。人心陷溺。说尧舜之道德。则曰犹天之不可升也。言尧舜之事业。则曰日月之不可及也。有如曹交之食粟而已。焉能学尧舜也。有如汉武之内多欲者。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也。天运循环。宋德隆盛。濂洛群哲。继
其容则马裾而已。自弃乎良知。而不以尧而为法。自暴乎良能。而不以舜而为期。则后于尧而其果有尧乎。后于舜而其果有舜乎。执事之疑。无足多辨。而苟求尧舜之圣于尧舜之后。则愚有所可證者矣。何以明其然也。承精一之心法。而孜孜于文命敷四之际者圣矣。夏禹则是岂非夏之尧舜乎。体执中之圣道。而慄慄于制礼制义之时者允矣。殷汤则是岂非殷之尧舜乎。文王之至德。莫非德尧舜之德而以为文者也。武成之气像。莫非像尧舜之像而以为武者也。以至伊傅周召之臣。亦皆以尧舜之道而为圣者则盛矣。殷周之尧舜。一何多也。至于吾夫子。则以出类之圣。祖述尧舜。以拔萃之圣。贤于尧舜。皓皓之德。实无间于荡荡。高坚之道。自有光于魏巍。则尧舜非夫子乎。夫子非尧舜乎。至若沂水春风。万物同流者。点也气像。便是尧舜气像也。战国荆榛。必称尧舜者。亚圣性善。即是尧舜之性善也。自此以后。则世道不淑。人心陷溺。说尧舜之道德。则曰犹天之不可升也。言尧舜之事业。则曰日月之不可及也。有如曹交之食粟而已。焉能学尧舜也。有如汉武之内多欲者。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也。天运循环。宋德隆盛。濂洛群哲。继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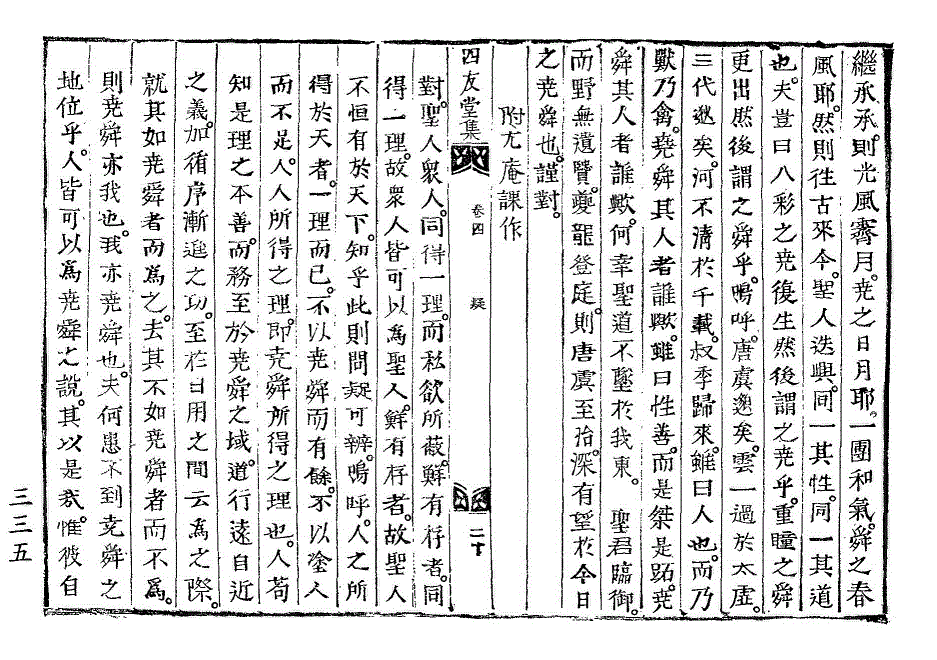 继承承。则光风霁月。尧之日月耶。一团和气。舜之春风耶。然则往古来今。圣人迭兴。同一其性。同一其道也。夫岂曰八彩之尧复生然后谓之尧乎。重瞳之舜更出然后谓之舜乎。呜呼。唐虞邈矣。云一过于太虚。三代逖矣。河不清于千载。叔季归来。虽曰人也。而乃兽乃禽。尧舜其人者谁欤。虽曰性善。而是桀是蹠。尧舜其人者谁欤。何幸圣道不坠于我东。 圣君临御。而野无遗贤。夔龙登庭。则唐虞至治。深有望于今日之尧舜也。谨对。
继承承。则光风霁月。尧之日月耶。一团和气。舜之春风耶。然则往古来今。圣人迭兴。同一其性。同一其道也。夫岂曰八彩之尧复生然后谓之尧乎。重瞳之舜更出然后谓之舜乎。呜呼。唐虞邈矣。云一过于太虚。三代逖矣。河不清于千载。叔季归来。虽曰人也。而乃兽乃禽。尧舜其人者谁欤。虽曰性善。而是桀是蹠。尧舜其人者谁欤。何幸圣道不坠于我东。 圣君临御。而野无遗贤。夔龙登庭。则唐虞至治。深有望于今日之尧舜也。谨对。附尤庵课作
对。圣人众人。同得一理。而私欲所蔽。鲜有存者。同得一理。故众人皆可以为圣人。鲜有存者。故圣人不恒有于天下。知乎此则问疑可辨。呜呼。人之所得于天者。一理而已。不以尧舜而有馀。不以涂人而不足。人人所得之理。即尧舜所得之理也。人苟知是理之本善。而务至于尧舜之域。道行远自近之义。加循序渐进之功。至于日用之间云为之际。就其如尧舜者而为之。去其不如尧舜者而不为。则尧舜亦我也。我亦尧舜也。夫何患不到尧舜之地位乎。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其以是哉。惟彼自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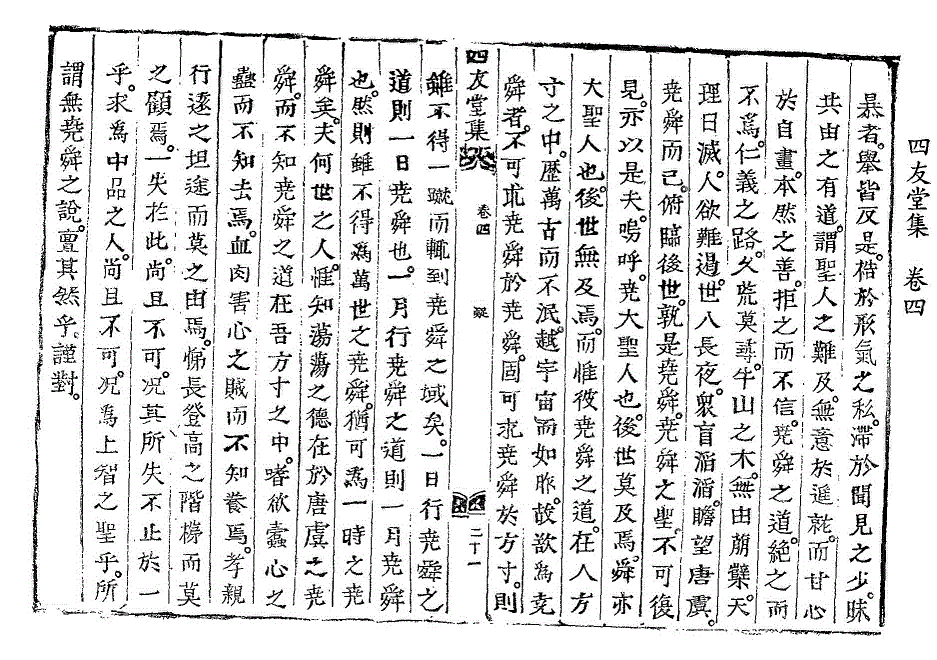 暴者。举皆反是。梏于形气之私。滞于闻见之少。昧共由之有道。谓圣人之难及。无意于进就。而甘心于自画。本然之善。拒之而不信。尧舜之道。绝之而不为。仁义之路。久荒莫寻。牛山之木。无由萌蘖。天理日灭。人欲难遏。世入长夜。众盲滔滔。瞻望唐虞。尧舜而已。俯临后世。孰是尧舜。尧舜之圣。不可复见。亦以是夫。呜呼。尧大圣人也。后世莫及焉。舜亦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而惟彼尧舜之道。在人方寸之中。历万古而不泯。越宇宙而如昨。故欲为尧舜者。不可求尧舜于尧舜。固可求尧舜于方寸。则虽不得一蹴而辄到尧舜之域矣。一日行尧舜之道则一日尧舜也。一月行尧舜之道则一月尧舜也。然则虽不得为万世之尧舜。犹可为一时之尧舜矣。夫何世之人。惟知荡荡之德在于唐虞之尧舜。而不知尧舜之道在吾方寸之中。嗜欲蠹心之蛊而不知去焉。血肉害心之贼而不知养焉。孝亲行远之坦途而莫之由焉。悌长登高之阶梯而莫之顾焉。一失于此。尚且不可。况其所失不止于一乎。求为中品之人。尚且不可。况为上智之圣乎。所谓无尧舜之说。亶其然乎。谨对。
暴者。举皆反是。梏于形气之私。滞于闻见之少。昧共由之有道。谓圣人之难及。无意于进就。而甘心于自画。本然之善。拒之而不信。尧舜之道。绝之而不为。仁义之路。久荒莫寻。牛山之木。无由萌蘖。天理日灭。人欲难遏。世入长夜。众盲滔滔。瞻望唐虞。尧舜而已。俯临后世。孰是尧舜。尧舜之圣。不可复见。亦以是夫。呜呼。尧大圣人也。后世莫及焉。舜亦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而惟彼尧舜之道。在人方寸之中。历万古而不泯。越宇宙而如昨。故欲为尧舜者。不可求尧舜于尧舜。固可求尧舜于方寸。则虽不得一蹴而辄到尧舜之域矣。一日行尧舜之道则一日尧舜也。一月行尧舜之道则一月尧舜也。然则虽不得为万世之尧舜。犹可为一时之尧舜矣。夫何世之人。惟知荡荡之德在于唐虞之尧舜。而不知尧舜之道在吾方寸之中。嗜欲蠹心之蛊而不知去焉。血肉害心之贼而不知养焉。孝亲行远之坦途而莫之由焉。悌长登高之阶梯而莫之顾焉。一失于此。尚且不可。况其所失不止于一乎。求为中品之人。尚且不可。况为上智之圣乎。所谓无尧舜之说。亶其然乎。谨对。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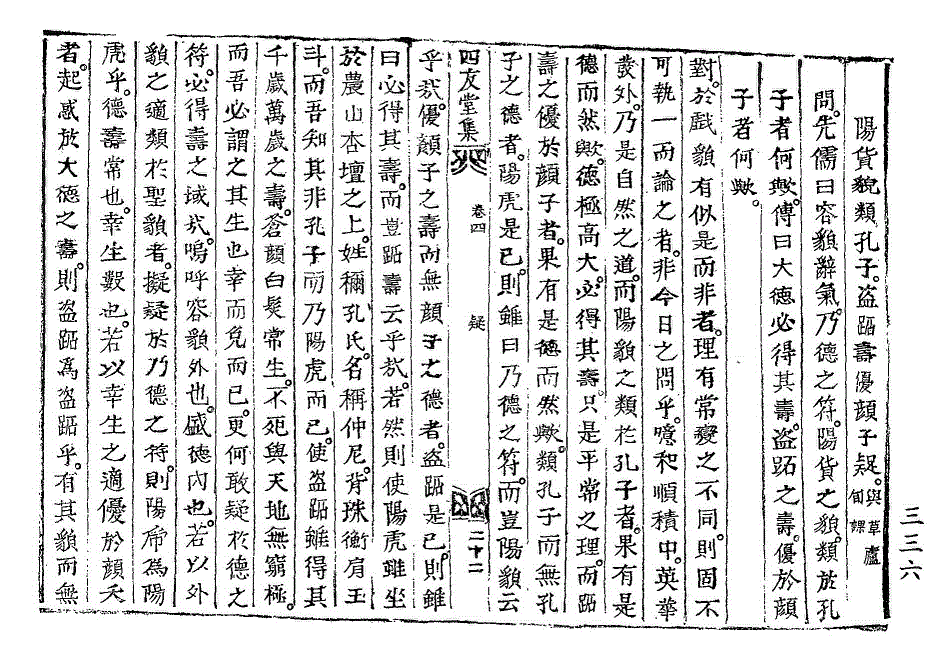 阳货貌类孔子。盗蹠寿优颜子疑。(与草庐旬课)
阳货貌类孔子。盗蹠寿优颜子疑。(与草庐旬课)问。先儒曰容貌辞气。乃德之符。阳货之貌。类于孔子者何欤。传曰大德必得其寿。盗蹠之寿。优于颜子者何欤。
对。于戏貌有似是而非者。理有常变之不同。则固不可执一而论之者。非今日之问乎。噫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乃是自然之道。而阳貌之类于孔子者。果有是德而然欤。德极高大。必得其寿。只是平常之理。而蹠寿之优于颜子者。果有是德而然欤。类孔子而无孔子之德者。阳虎是已。则虽曰乃德之符。而岂阳貌云乎哉。优颜子之寿而无颜子之德者。盗蹠是已。则虽曰必得其寿。而岂蹠寿云乎哉。若然则使阳虎虽坐于农山杏坛之上。姓称孔氏。名称仲尼。背珠衡肩玉斗。而吾知其非孔子而乃阳虎而已。使盗蹠虽得其千岁万岁之寿。苍颜白发常生。不死与天地无穷极。而吾必谓之其生也幸而免而已。更何敢疑于德之符。必得寿之域哉。呜呼容貌外也。盛德内也。若以外貌之适类于圣貌者。拟疑于乃德之符。则阳虎为阳虎乎。德寿常也。幸生数也。若以幸生之适优于颜夭者。起惑于大德之寿。则盗蹠为盗蹠乎。有其貌而无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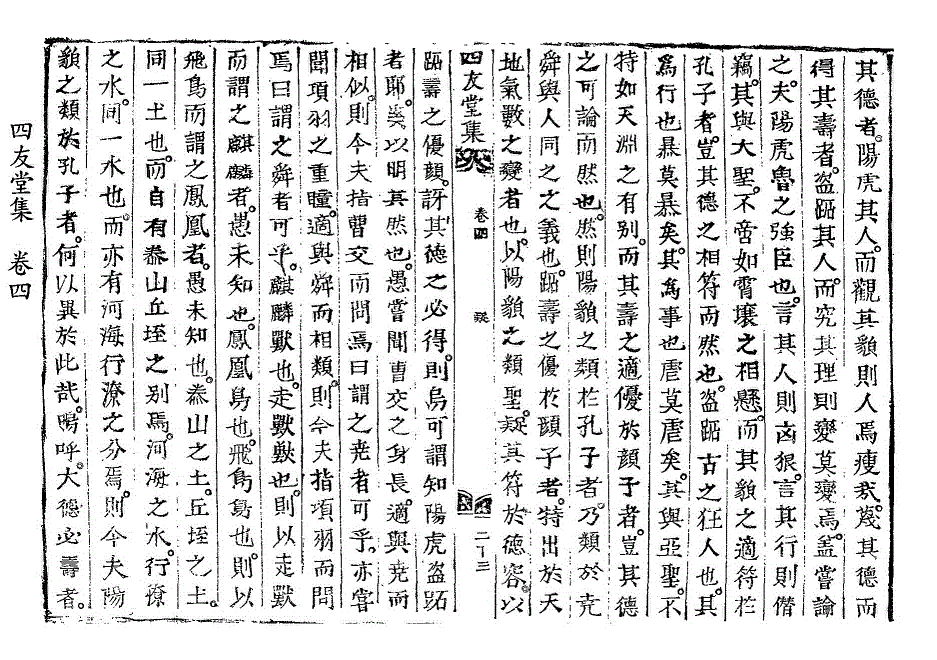 其德者。阳虎其人。而观其貌则人焉瘦哉。蔑其德而得其寿者。盗蹠其人。而究其理则变莫变焉。盖尝论之。夫阳虎鲁之强臣也。言其人则凶狠。言其行则僭窃。其与大圣。不啻如霄壤之相悬。而其貌之适符于孔子者。岂其德之相符而然也。盗蹠古之狂人也。其为行也暴莫暴矣。其为事也虐莫虐矣。其与亚圣。不特如天渊之有别。而其寿之适优于颜子者。岂其德之可论而然也。然则阳貌之类于孔子者。乃类于尧舜与人同之之义也。蹠寿之优于颜子者。特出于天地气数之变者也。以阳貌之类圣。疑其符于德容。以蹠寿之优颜。讶其德之必得。则乌可谓知阳虎盗蹠者耶。奚以明其然也。愚尝闻曹交之身长。适与尧而相似。则今夫指曹交而问焉曰谓之尧者可乎。亦尝闻项羽之重瞳。适与舜而相类。则今夫指项羽而问焉曰谓之舜者可乎。麒麟兽也。走兽兽也。则以走兽而谓之麒麟者。愚未知也。凤凰鸟也。飞鸟鸟也。则以飞鸟而谓之凤凰者。愚未知也。泰山之土。丘垤之土。同一土也。而自有泰山丘垤之别焉。河海之水。行潦之水。同一水也。而亦有河海行潦之分焉。则今夫阳貌之类于孔子者。何以异于此哉。呜呼。大德必寿者。
其德者。阳虎其人。而观其貌则人焉瘦哉。蔑其德而得其寿者。盗蹠其人。而究其理则变莫变焉。盖尝论之。夫阳虎鲁之强臣也。言其人则凶狠。言其行则僭窃。其与大圣。不啻如霄壤之相悬。而其貌之适符于孔子者。岂其德之相符而然也。盗蹠古之狂人也。其为行也暴莫暴矣。其为事也虐莫虐矣。其与亚圣。不特如天渊之有别。而其寿之适优于颜子者。岂其德之可论而然也。然则阳貌之类于孔子者。乃类于尧舜与人同之之义也。蹠寿之优于颜子者。特出于天地气数之变者也。以阳貌之类圣。疑其符于德容。以蹠寿之优颜。讶其德之必得。则乌可谓知阳虎盗蹠者耶。奚以明其然也。愚尝闻曹交之身长。适与尧而相似。则今夫指曹交而问焉曰谓之尧者可乎。亦尝闻项羽之重瞳。适与舜而相类。则今夫指项羽而问焉曰谓之舜者可乎。麒麟兽也。走兽兽也。则以走兽而谓之麒麟者。愚未知也。凤凰鸟也。飞鸟鸟也。则以飞鸟而谓之凤凰者。愚未知也。泰山之土。丘垤之土。同一土也。而自有泰山丘垤之别焉。河海之水。行潦之水。同一水也。而亦有河海行潦之分焉。则今夫阳貌之类于孔子者。何以异于此哉。呜呼。大德必寿者。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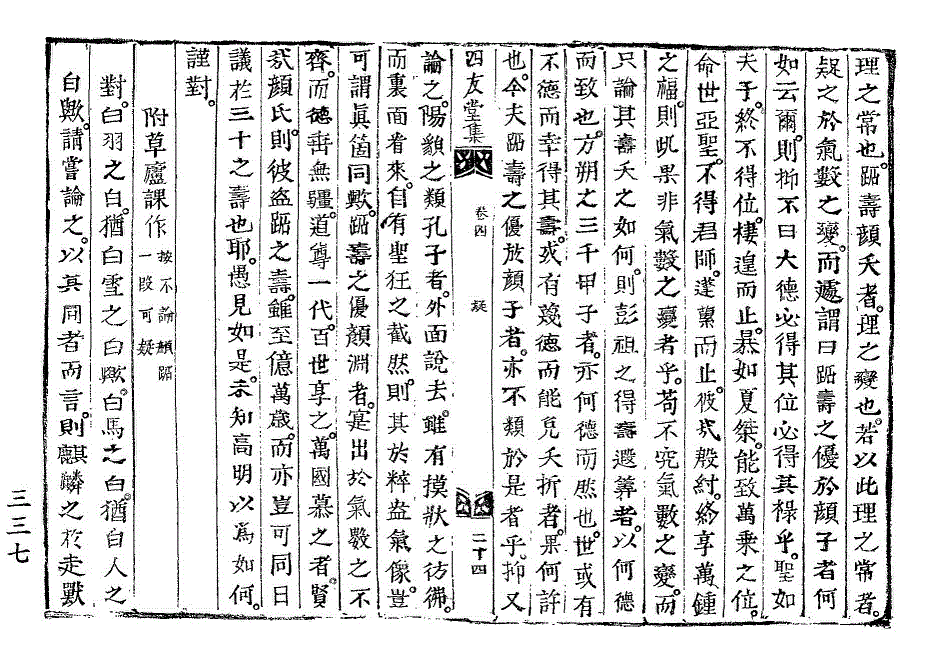 理之常也。蹠寿颜夭者。理之变也。若以此理之常者。疑之于气数之变。而遽谓曰蹠寿之优于颜子者何如云尔。则抑不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乎。圣如夫子。终不得位。栖遑而止。暴如夏桀。能致万乘之位。命世亚圣。不得君师。蓬蔂而止。彼哉殷纣。终享万钟之福。则此果非气数之变者乎。苟不究气数之变。而只论其寿夭之如何。则彭祖之得寿遐算者。以何德而致也。方朔之三千甲子者。亦何德而然也。世或有不德而幸得其寿。或有蔑德而能免夭折者。果何许也。今夫蹠寿之优于颜子者。亦不类于是者乎。抑又论之。阳貌之类孔子者。外面说去。虽有摸状之彷佛。而里面看来。自有圣狂之截然。则其于粹盎气像。岂可谓真个同欤。蹠寿之优颜渊者。寔出于气数之不齐。而德垂无疆。道尊一代。百世享之。万国慕之者。贤哉颜氏。则彼盗蹠之寿。虽至亿万岁。而亦岂可同日议于三十之寿也耶。愚见如是。未知高明以为如何。谨对。
理之常也。蹠寿颜夭者。理之变也。若以此理之常者。疑之于气数之变。而遽谓曰蹠寿之优于颜子者何如云尔。则抑不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乎。圣如夫子。终不得位。栖遑而止。暴如夏桀。能致万乘之位。命世亚圣。不得君师。蓬蔂而止。彼哉殷纣。终享万钟之福。则此果非气数之变者乎。苟不究气数之变。而只论其寿夭之如何。则彭祖之得寿遐算者。以何德而致也。方朔之三千甲子者。亦何德而然也。世或有不德而幸得其寿。或有蔑德而能免夭折者。果何许也。今夫蹠寿之优于颜子者。亦不类于是者乎。抑又论之。阳貌之类孔子者。外面说去。虽有摸状之彷佛。而里面看来。自有圣狂之截然。则其于粹盎气像。岂可谓真个同欤。蹠寿之优颜渊者。寔出于气数之不齐。而德垂无疆。道尊一代。百世享之。万国慕之者。贤哉颜氏。则彼盗蹠之寿。虽至亿万岁。而亦岂可同日议于三十之寿也耶。愚见如是。未知高明以为如何。谨对。附草庐课作(按不论颜蹠一段可疑)
对。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欤。白马之白。犹白人之白欤。请尝论之。以其同者而言。则麒麟之于走兽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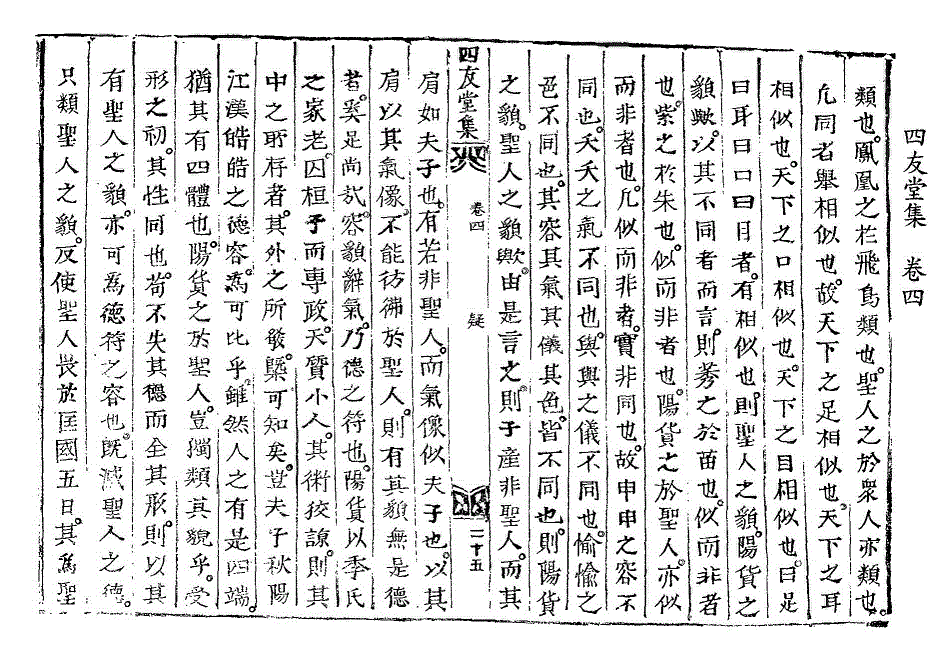 类也。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众人亦类也。凡同者举相似也。故天下之足相似也。天下之耳相似也。天下之口相似也。天下之目相似也。曰足曰耳曰口曰目者。有相似也。则圣人之貌。阳货之貌欤。以其不同者而言。则莠之于苗也。似而非者也。紫之于朱也。似而非者也。阳货之于圣人。亦似而非者也。凡似而非者。实非同也。故申申之容不同也。夭夭之气不同也。与与之仪不同也。愉愉之色不同也。其容其气其仪其色。皆不同也。则阳货之貌。圣人之貌欤。由是言之。则子产非圣人。而其肩如夫子也。有若非圣人。而气像似夫子也。以其肩以其气像。不能彷佛于圣人。则有其貌无是德者。奚足尚哉。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阳货以季氏之家老。囚桓子而专政。天质小人。其𧗱狡谅。则其中之所存者。其外之所发。槩可知矣。岂夫子秋阳江汉皓皓之德容。为可比乎。虽然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阳货之于圣人。岂独类其貌乎。受形之初。其性同也。苟不失其德而全其形。则以其有圣人之貌。亦可为德符之容也。既灭圣人之德。只类圣人之貌。反使圣人畏于匡国五日。其为圣
类也。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众人亦类也。凡同者举相似也。故天下之足相似也。天下之耳相似也。天下之口相似也。天下之目相似也。曰足曰耳曰口曰目者。有相似也。则圣人之貌。阳货之貌欤。以其不同者而言。则莠之于苗也。似而非者也。紫之于朱也。似而非者也。阳货之于圣人。亦似而非者也。凡似而非者。实非同也。故申申之容不同也。夭夭之气不同也。与与之仪不同也。愉愉之色不同也。其容其气其仪其色。皆不同也。则阳货之貌。圣人之貌欤。由是言之。则子产非圣人。而其肩如夫子也。有若非圣人。而气像似夫子也。以其肩以其气像。不能彷佛于圣人。则有其貌无是德者。奚足尚哉。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阳货以季氏之家老。囚桓子而专政。天质小人。其𧗱狡谅。则其中之所存者。其外之所发。槩可知矣。岂夫子秋阳江汉皓皓之德容。为可比乎。虽然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阳货之于圣人。岂独类其貌乎。受形之初。其性同也。苟不失其德而全其形。则以其有圣人之貌。亦可为德符之容也。既灭圣人之德。只类圣人之貌。反使圣人畏于匡国五日。其为圣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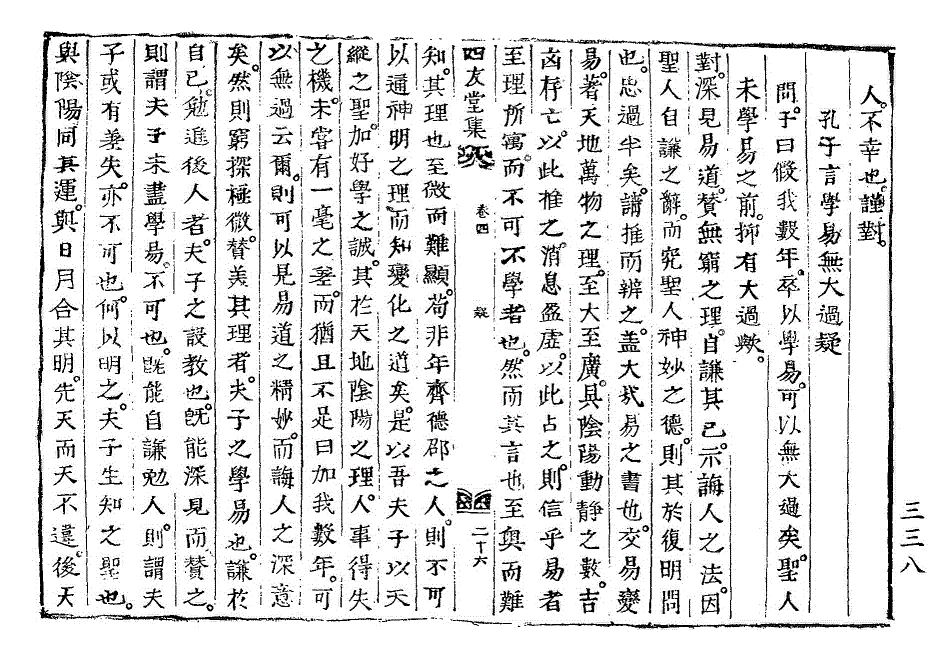 人。不幸也。谨对。
人。不幸也。谨对。孔子言学易无大过疑
问。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圣人未学易之前。抑有大过欤。
对。深见易道。赞无穷之理。自谦其己。示诲人之法。因圣人自谦之辞。而究圣人神妙之德。则其于复明问也。忠过半矣。请推而辨之。盖大哉易之书也。交易变易。著天地万物之理。至大至广。具阴阳动静之数。吉凶存亡。以此推之。消息盈虚。以此占之。则信乎易者至理所寓。而不可不学者也。然而其言也至奥而难知。其理也至微而难显。苟非年齐德卲之人。则不可以通神明之理而知变化之道矣。是以吾夫子以天纵之圣。加好学之诚。其于天地阴阳之理。人事得失之机。未尝有一毫之差。而犹且不足曰加我数年。可以无过云尔。则可以见易道之精妙。而诲人之深意矣。然则穷探极微。赞美其理者。夫子之学易也。谦于自己。勉进后人者。夫子之设教也。既能深见而赞之。则谓夫子未尽学易。不可也。既能自谦勉人。则谓夫子或有差失。亦不可也。何以明之。夫子生知之圣也。与阴阳同其运。与日月合其明。先天而天不违。后天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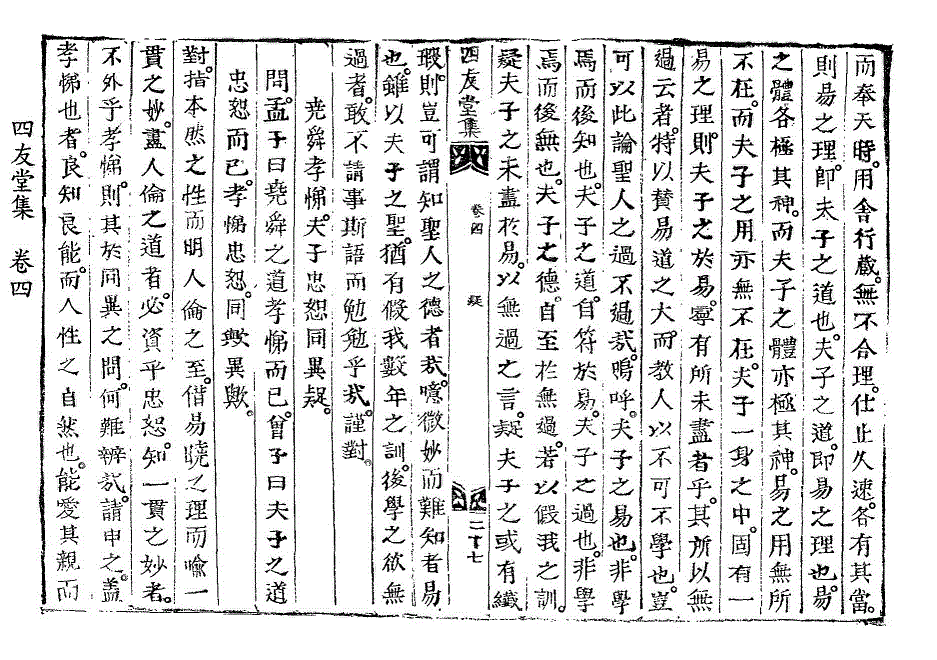 而奉天时。用舍行藏。无不合理。仕止久速。各有其当。则易之理。即夫子之道也。夫子之道。即易之理也。易之体各极其神。而夫子之体亦极其神。易之用无所不在。而夫子之用亦无不在。夫子一身之中。固有一易之理。则夫子之于易。宁有所未尽者乎。其所以无过云者。特以赞易道之大。而教人以不可不学也。岂可以此论圣人之过不过哉。呜呼。夫子之易也。非学焉而后知也。夫子之道。自符于易。夫子之过也。非学焉而后无也。夫子之德。自至于无过。若以假我之训。疑夫子之未尽于易。以无过之言。疑夫子之或有纤瑕。则岂可谓知圣人之德者哉。噫微妙而难知者易也。虽以夫子之圣。犹有假我数年之训。后学之欲无过者。敢不请事斯语而勉勉乎哉。谨对。
而奉天时。用舍行藏。无不合理。仕止久速。各有其当。则易之理。即夫子之道也。夫子之道。即易之理也。易之体各极其神。而夫子之体亦极其神。易之用无所不在。而夫子之用亦无不在。夫子一身之中。固有一易之理。则夫子之于易。宁有所未尽者乎。其所以无过云者。特以赞易道之大。而教人以不可不学也。岂可以此论圣人之过不过哉。呜呼。夫子之易也。非学焉而后知也。夫子之道。自符于易。夫子之过也。非学焉而后无也。夫子之德。自至于无过。若以假我之训。疑夫子之未尽于易。以无过之言。疑夫子之或有纤瑕。则岂可谓知圣人之德者哉。噫微妙而难知者易也。虽以夫子之圣。犹有假我数年之训。后学之欲无过者。敢不请事斯语而勉勉乎哉。谨对。尧舜孝悌。夫子忠恕同异疑。
问。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孝悌忠恕。同欤异欤。
对。指本然之性而明人伦之至。借易晓之理而喻一贯之妙。尽人伦之道者。必资乎忠恕。知一贯之妙者。不外乎孝悌。则其于同异之问。何难辨哉。请申之。盖孝悌也者。良知良能。而人性之自然也。能爱其亲而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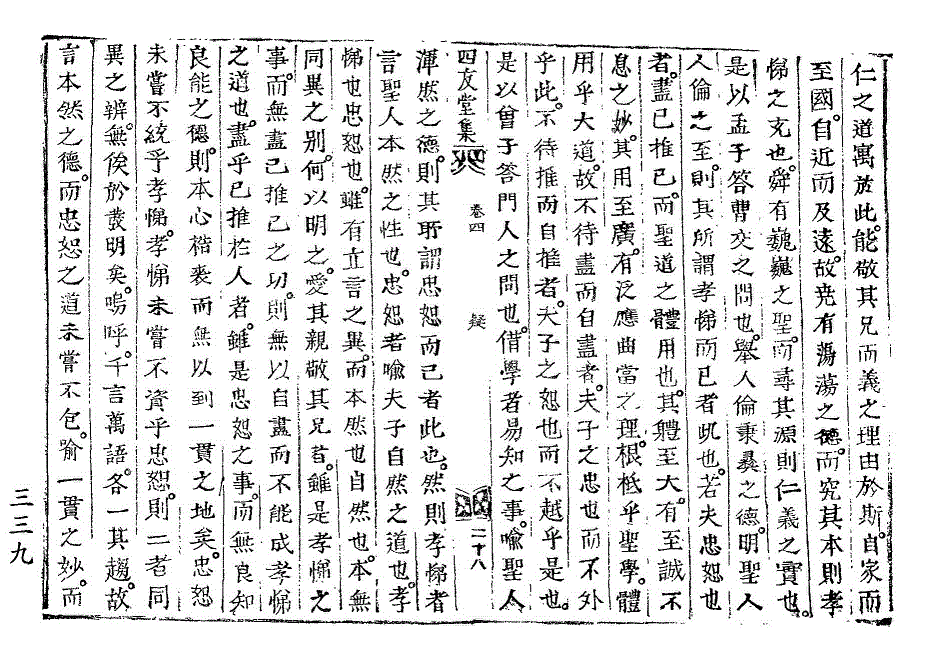 仁之道寓于此。能敬其兄而义之理由于斯。自家而至国。自近而及远。故尧有荡荡之德。而究其本则孝悌之充也。舜有巍巍之圣。而寻其源则仁义之实也。是以孟子答曹交之问也。举人伦秉彝之德。明圣人人伦之至。则其所谓孝悌而已者此也。若夫忠恕也者。尽己推己。而圣道之体用也。其体至大。有至诚不息之妙。其用至广。有泛应曲当之理。根柢乎圣学。体用乎大道。故不待尽而自尽者。夫子之忠也而不外乎此。不待推而自推者。夫子之恕也而不越乎是也。是以曾子答门人之问也。借学者易知之事。喻圣人浑然之德。则其所谓忠恕而已者此也。然则孝悌者言圣人本然之性也。忠恕者喻夫子自然之道也。孝悌也忠恕也。虽有立言之异。而本然也自然也。本无同异之别。何以明之。爱其亲敬其兄者。虽是孝悌之事。而无尽己推己之功。则无以自尽而不能成孝悌之道也。尽乎己推于人者。虽是忠恕之事。而无良知良能之德。则本心梏丧而无以到一贯之地矣。忠恕未尝不统乎孝悌。孝悌未尝不资乎忠恕。则二者同异之辨。无俟于发明矣。呜呼。千言万语。各一其趋。故言本然之德。而忠恕之道未尝不包。喻一贯之妙。而
仁之道寓于此。能敬其兄而义之理由于斯。自家而至国。自近而及远。故尧有荡荡之德。而究其本则孝悌之充也。舜有巍巍之圣。而寻其源则仁义之实也。是以孟子答曹交之问也。举人伦秉彝之德。明圣人人伦之至。则其所谓孝悌而已者此也。若夫忠恕也者。尽己推己。而圣道之体用也。其体至大。有至诚不息之妙。其用至广。有泛应曲当之理。根柢乎圣学。体用乎大道。故不待尽而自尽者。夫子之忠也而不外乎此。不待推而自推者。夫子之恕也而不越乎是也。是以曾子答门人之问也。借学者易知之事。喻圣人浑然之德。则其所谓忠恕而已者此也。然则孝悌者言圣人本然之性也。忠恕者喻夫子自然之道也。孝悌也忠恕也。虽有立言之异。而本然也自然也。本无同异之别。何以明之。爱其亲敬其兄者。虽是孝悌之事。而无尽己推己之功。则无以自尽而不能成孝悌之道也。尽乎己推于人者。虽是忠恕之事。而无良知良能之德。则本心梏丧而无以到一贯之地矣。忠恕未尝不统乎孝悌。孝悌未尝不资乎忠恕。则二者同异之辨。无俟于发明矣。呜呼。千言万语。各一其趋。故言本然之德。而忠恕之道未尝不包。喻一贯之妙。而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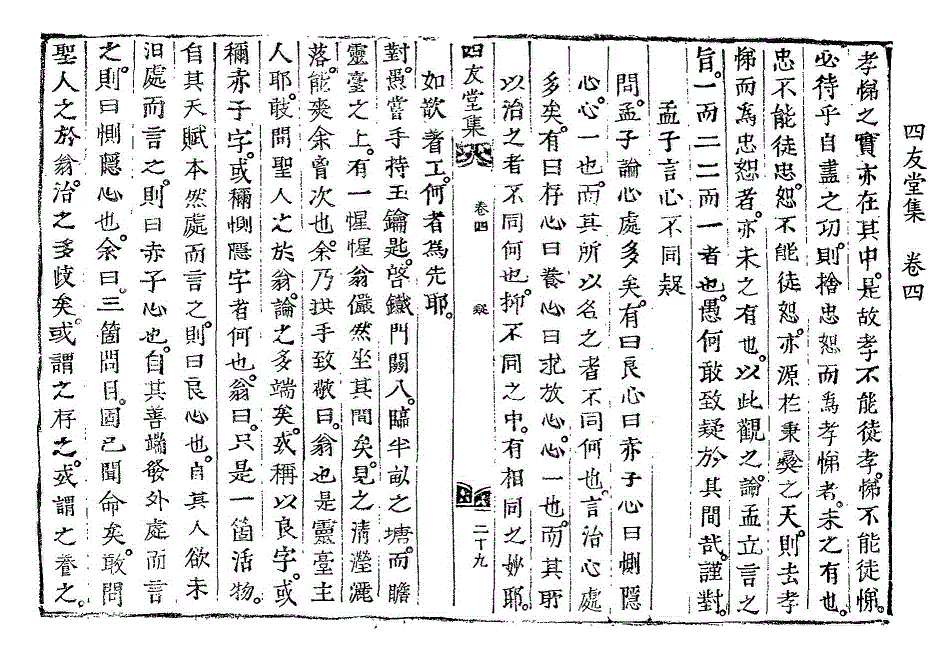 孝悌之实亦在其中。是故孝不能徒孝。悌不能徒悌。必待乎自尽之功。则舍忠恕而为孝悌者。未之有也。忠不能徒忠。恕不能徒恕。亦源于秉彝之天。则去孝悌而为忠恕者。亦未之有也。以此观之。论孟立言之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何敢致疑于其间哉。谨对。
孝悌之实亦在其中。是故孝不能徒孝。悌不能徒悌。必待乎自尽之功。则舍忠恕而为孝悌者。未之有也。忠不能徒忠。恕不能徒恕。亦源于秉彝之天。则去孝悌而为忠恕者。亦未之有也。以此观之。论孟立言之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何敢致疑于其间哉。谨对。孟子言心不同疑
问。孟子论心处多矣。有曰良心曰赤子心曰恻隐心。心一也。而其所以名之者不同何也。言治心处多矣。有曰存心曰养心曰求放心。心一也。而其所以治之者不同何也。抑不同之中。有相同之妙耶。如欲着工。何者为先耶。
对。愚尝手持玉钥匙。启铁门关入。临半亩之塘。而瞻灵台之上。有一惺惺翁俨然坐其间矣。见之清滢洒落。能爽余胸次也。余乃拱手致敬曰。翁也是灵台主人耶。敢问圣人之于翁。论之多端矣。或称以良字。或称赤子字。或称恻隐字者何也。翁曰。只是一个活物。自其天赋本然处而言之。则曰良心也。自其人欲未汩处而言之。则曰赤子心也。自其善端发外处而言之。则曰恻隐心也。余曰。三个问目。固已闻命矣。敢问圣人之于翁。治之多歧矣。或谓之存之。或谓之养之。
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40L 页
 或谓之求之者何也。翁曰。只是一个治法。随其出入无常处而治之。则操之为存心矣。随其人欲交攻处而治之。则遏之为养心矣。随其游骑出远处而治之。则索之为求放心也。余曰。三条治法。亦既闻命矣。敢问其曰存曰养曰求之中。当先着甚么也。曰先贤有言曰知其病处。便是去病之剂也。又曰不远复为三字符。能知其放。则这是知病也。知而求之。则这是良剂也。既能求而反之。则其所谓不远复。而存养之妙。亦不离乎其中也。虽然要不出彻头彻尾底敬字上工夫而已矣。余乃磬折而退。眷眷服膺而不失矣。今来礼围。恭承明问。固知翁之言。为此日准备也。请以翁之言。敬焚一办香可乎。乃言曰天以浑然一太极。赋予我人。而有此虚灵不昧之物。使之主宰一身而酬酢万变也。其所谓良心者。以其纯粹无杂。而烱若水镜之清圆也。其所谓赤子心者。以其纯一无伪。而姑无意欲之萌芽也。其所谓恻隐心者。以其善端随感。而蔼如春物之嘘茁也。此所以一心之三易其名也。然而神明之妙。时出时入而莫知其乡。则不可不操而存此也。形色之欲。以臭以味而丧其本真。则不可不遏而养此也。情车之奔。之南之北而靡有其止。
或谓之求之者何也。翁曰。只是一个治法。随其出入无常处而治之。则操之为存心矣。随其人欲交攻处而治之。则遏之为养心矣。随其游骑出远处而治之。则索之为求放心也。余曰。三条治法。亦既闻命矣。敢问其曰存曰养曰求之中。当先着甚么也。曰先贤有言曰知其病处。便是去病之剂也。又曰不远复为三字符。能知其放。则这是知病也。知而求之。则这是良剂也。既能求而反之。则其所谓不远复。而存养之妙。亦不离乎其中也。虽然要不出彻头彻尾底敬字上工夫而已矣。余乃磬折而退。眷眷服膺而不失矣。今来礼围。恭承明问。固知翁之言。为此日准备也。请以翁之言。敬焚一办香可乎。乃言曰天以浑然一太极。赋予我人。而有此虚灵不昧之物。使之主宰一身而酬酢万变也。其所谓良心者。以其纯粹无杂。而烱若水镜之清圆也。其所谓赤子心者。以其纯一无伪。而姑无意欲之萌芽也。其所谓恻隐心者。以其善端随感。而蔼如春物之嘘茁也。此所以一心之三易其名也。然而神明之妙。时出时入而莫知其乡。则不可不操而存此也。形色之欲。以臭以味而丧其本真。则不可不遏而养此也。情车之奔。之南之北而靡有其止。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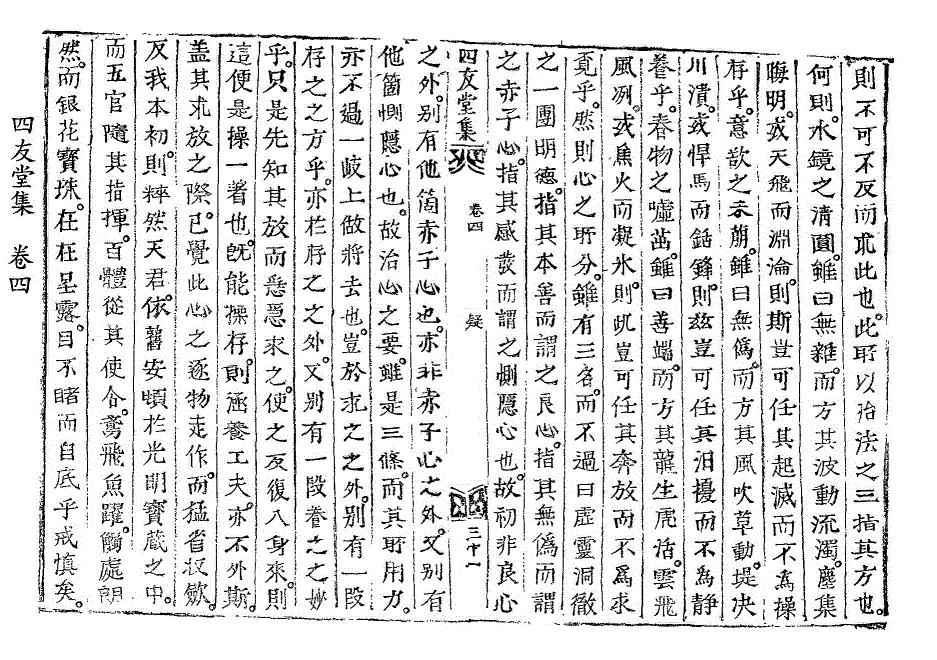 则不可不反而求此也。此所以治法之三指其方也。何则。水镜之清圆。虽曰无杂。而方其波动流浊。尘集晦明。或天飞而渊沦。则斯岂可任其起灭而不为操存乎。意欲之未萌。虽曰无伪。而方其风吹草动。堤决川溃。或悍马而铦锋。则玆岂可任其汩扰而不为静养乎。春物之嘘茁。虽曰善端。而方其龙生虎活。云飞风冽。或焦火而凝冰。则此岂可任其奔放而不为求觅乎。然则心之所分。虽有三名。而不过曰虚灵洞彻之一团明德。指其本善而谓之良心。指其无伪而谓之赤子心。指其感发而谓之恻隐心也。故初非良心之外。别有他个赤子心也。亦非赤子心之外。又别有他个恻隐心也。故治心之要。虽是三条。而其所用力。亦不过一岐上做将去也。岂于求之之外。别有一段存之之方乎。亦于存之之外。又别有一段养之之妙乎。只是先知其放而急急求之。使之反复入身来。则这便是操一着也。既能操存。则涵养工夫。亦不外斯。盖其求放之际。已觉此心之逐物走作。而猛省收敛。反我本初。则粹然天君。依旧安顿于光明宝藏之中。而五官随其指挥。百体从其使令。鸢飞鱼跃。触处朗然。而银花宝珠。在在呈露。目不睹而自底乎戒慎矣。
则不可不反而求此也。此所以治法之三指其方也。何则。水镜之清圆。虽曰无杂。而方其波动流浊。尘集晦明。或天飞而渊沦。则斯岂可任其起灭而不为操存乎。意欲之未萌。虽曰无伪。而方其风吹草动。堤决川溃。或悍马而铦锋。则玆岂可任其汩扰而不为静养乎。春物之嘘茁。虽曰善端。而方其龙生虎活。云飞风冽。或焦火而凝冰。则此岂可任其奔放而不为求觅乎。然则心之所分。虽有三名。而不过曰虚灵洞彻之一团明德。指其本善而谓之良心。指其无伪而谓之赤子心。指其感发而谓之恻隐心也。故初非良心之外。别有他个赤子心也。亦非赤子心之外。又别有他个恻隐心也。故治心之要。虽是三条。而其所用力。亦不过一岐上做将去也。岂于求之之外。别有一段存之之方乎。亦于存之之外。又别有一段养之之妙乎。只是先知其放而急急求之。使之反复入身来。则这便是操一着也。既能操存。则涵养工夫。亦不外斯。盖其求放之际。已觉此心之逐物走作。而猛省收敛。反我本初。则粹然天君。依旧安顿于光明宝藏之中。而五官随其指挥。百体从其使令。鸢飞鱼跃。触处朗然。而银花宝珠。在在呈露。目不睹而自底乎戒慎矣。四友堂先生集卷之四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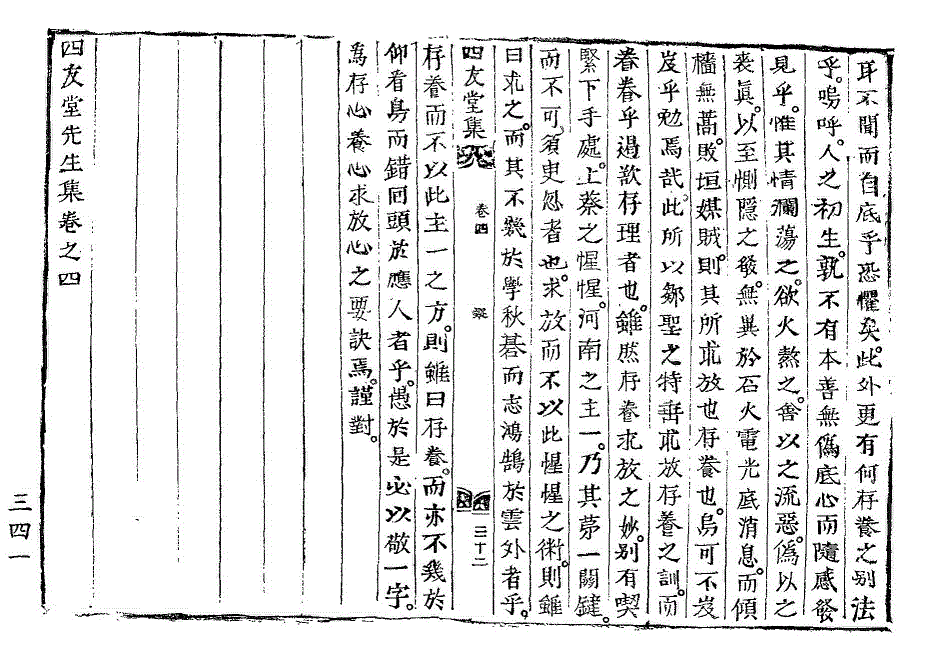 耳不闻而自底乎恐惧矣。此外更有何存养之别法乎。呜呼。人之初生。孰不有本善无伪底心而随感发见乎。惟其情澜荡之。欲火熬之。善以之流恶。伪以之丧真。以至恻隐之发。无异于石火电光底消息。而倾樯无蒿。败垣媒贼。则其所求放也存养也。乌可不岌岌乎勉焉哉。此所以邹圣之特垂求放存养之训。而眷眷乎遏欲存理者也。虽然存养求放之妙。别有吃紧下手处。上蔡之惺惺。河南之主一。乃其第一关键。而不可须臾忽者也。求放而不以此惺惺之𧗱。则虽曰求之。而其不几于学秋棋而志鸿鹄于云外者乎。存养而不以此主一之方。则虽曰存养。而亦不几于仰看鸟而错回头于应人者乎。愚于是必以敬一字。为存心养心求放心之要诀焉。谨对。
耳不闻而自底乎恐惧矣。此外更有何存养之别法乎。呜呼。人之初生。孰不有本善无伪底心而随感发见乎。惟其情澜荡之。欲火熬之。善以之流恶。伪以之丧真。以至恻隐之发。无异于石火电光底消息。而倾樯无蒿。败垣媒贼。则其所求放也存养也。乌可不岌岌乎勉焉哉。此所以邹圣之特垂求放存养之训。而眷眷乎遏欲存理者也。虽然存养求放之妙。别有吃紧下手处。上蔡之惺惺。河南之主一。乃其第一关键。而不可须臾忽者也。求放而不以此惺惺之𧗱。则虽曰求之。而其不几于学秋棋而志鸿鹄于云外者乎。存养而不以此主一之方。则虽曰存养。而亦不几于仰看鸟而错回头于应人者乎。愚于是必以敬一字。为存心养心求放心之要诀焉。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