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x 页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杂著
杂著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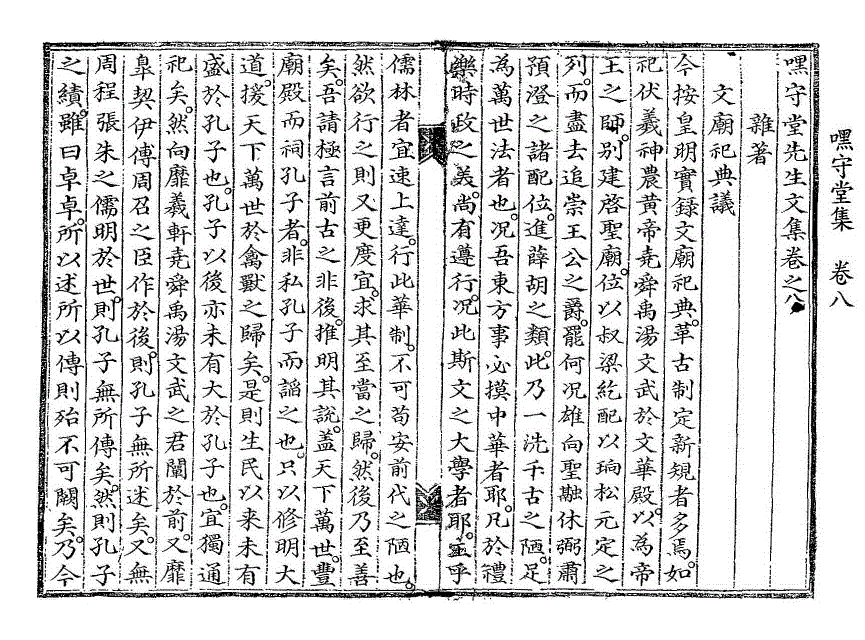 文庙祀典议
文庙祀典议今按皇明实录文庙祀典。革古制定新规者多焉。如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于文华殿。以为帝王之师。别建启圣庙。位以叔梁纥配以珦松元定之列。而尽去追崇王公之爵。罢何况雄向圣融休弼肃预澄之诸配位。进薛胡之类。此乃一洗千古之陋。足为万世法者也。况吾东方事必摸中华者耶。凡于礼乐时政之美。尚有遵行。况此斯文之大学者耶。主乎儒林者宜速上达。行此华制。不可苟安前代之陋也。然欲行之则又更度宜。求其至当之归。然后乃至善矣。吾请极言前古之非后。推明其说。盖天下万世。丰庙殿而祠孔子者。非私孔子而谄之也。只以修明大道。援天下万世于禽兽之归矣。是则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以后亦未有大于孔子也。宜独通祀矣。然向靡羲轩尧舜禹汤文武之君阐于前。又靡皋契伊傅周召之臣作于后。则孔子无所述矣。又无周程张朱之儒明于世。则孔子无所传矣。然则孔子之绩。虽曰卓卓。所以述所以传则殆不可阙矣。乃今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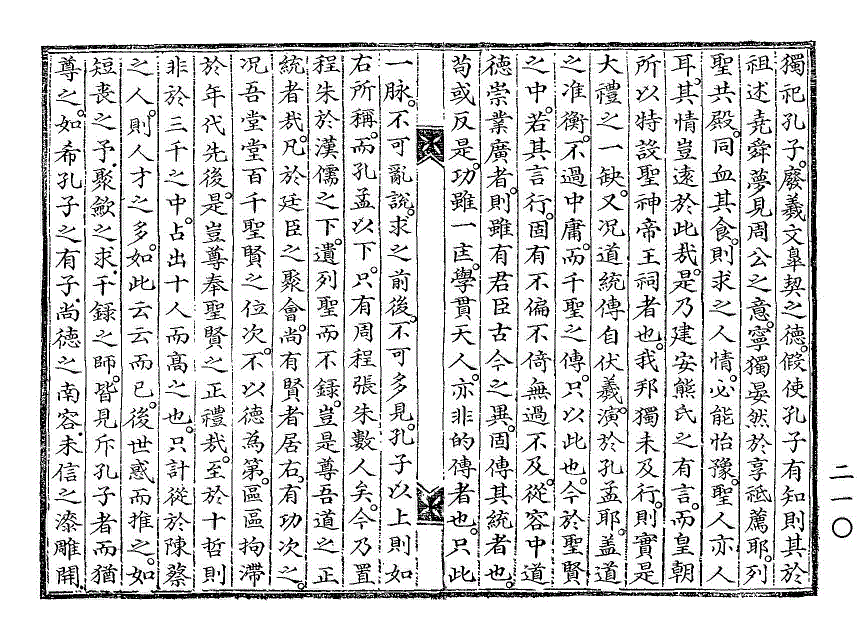 独祀孔子。废羲文皋契之德。假使孔子有知则其于祖述尧舜梦见周公之意。宁独晏然于享祗荐耶。列圣共殿。同血其食。则求之人情。必能怡豫。圣人亦人耳。其情岂远于此哉。是乃建安熊氏之有言。而皇朝所以特设圣神帝王祠者也。我邦独未及行。则实是大礼之一缺。又况道统传自伏羲。演于孔孟耶。盖道之准衡。不过中庸。而千圣之传。只以此也。今于圣贤之中。若其言行。固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从容中道德崇业广者。则虽有君臣古今之异。固传其统者也。苟或反是。功虽一匡。学贯天人。亦非的传者也。只此一脉。不可乱说。求之前后。不可多见。孔子以上则如右所称。而孔孟以下。只有周程张朱数人矣。今乃置程朱于汉儒之下。遗列圣而不录。岂是尊吾道之正统者哉。凡于廷臣之聚会。尚有贤者居右。有功次之。况吾堂堂百千圣贤之位次。不以德为第。区区拘滞于年代先后。是岂尊奉圣贤之正礼哉。至于十哲则非于三千之中。占出十人而高之也。只计从于陈蔡之人。则人才之多。如此云云而已。后世惑而推之。如短丧之予,聚敛之求,干录之师。皆见斥孔子者而犹尊之。如希孔子之有子,尚德之南容,未信之漆雕开,
独祀孔子。废羲文皋契之德。假使孔子有知则其于祖述尧舜梦见周公之意。宁独晏然于享祗荐耶。列圣共殿。同血其食。则求之人情。必能怡豫。圣人亦人耳。其情岂远于此哉。是乃建安熊氏之有言。而皇朝所以特设圣神帝王祠者也。我邦独未及行。则实是大礼之一缺。又况道统传自伏羲。演于孔孟耶。盖道之准衡。不过中庸。而千圣之传。只以此也。今于圣贤之中。若其言行。固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从容中道德崇业广者。则虽有君臣古今之异。固传其统者也。苟或反是。功虽一匡。学贯天人。亦非的传者也。只此一脉。不可乱说。求之前后。不可多见。孔子以上则如右所称。而孔孟以下。只有周程张朱数人矣。今乃置程朱于汉儒之下。遗列圣而不录。岂是尊吾道之正统者哉。凡于廷臣之聚会。尚有贤者居右。有功次之。况吾堂堂百千圣贤之位次。不以德为第。区区拘滞于年代先后。是岂尊奉圣贤之正礼哉。至于十哲则非于三千之中。占出十人而高之也。只计从于陈蔡之人。则人才之多。如此云云而已。后世惑而推之。如短丧之予,聚敛之求,干录之师。皆见斥孔子者而犹尊之。如希孔子之有子,尚德之南容,未信之漆雕开,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1H 页
 咏归之曾晰则皆见称孔子而犹卑之。是乃溺陈言而昧是非之故也。其亦误矣。且尧舜之道。孔子明之。孔子之道。七十子明之。孔孟之道。程朱明之。程朱之道。各其门人及宋元皇明之诸儒明之。若非孔子则尧舜之道熄矣。若非七十子则孔子之道断矣。若非程朱则孔孟之道废矣。若非门人诸儒则程朱之道塞矣。然则吾道自古及今。赖人显晦者如此。则程朱门人之功。虽有大细。一言一事。皆有关于道理。则孔子复起。尚可取矣。况后人之衣被其德者。当如何哉。若夫汉唐之儒。虽不识道。只研章句。然其圣谟。若无斯人收拾烬馀。则终必泯没无传矣。被发左衽。不疑何卜。今者不须律以大中之法。只许卫道之功。如夫子之许管仲。则亦一道也。中朝必尽罢之者。亦不弘矣。若吾东之祠法。有难晓者。凡吾箕子演九畴之学。始八条之法。今我国家。鸣以礼义之号。丕变蛮貊之俗者。莫非遗泽。则凡我民生。恩若昊天。家家设庙。尚且难报。通都大邑。亦不立祠。是若绥父母之鬼者。可谓无识之甚。而反曰帝王不可立庙。是则国家宗庙。亦皆废之。乃为礼矣。是乃愚夫之妄言。不足诘矣。今不祀箕子。还以谄佛求仙之孤云。独巍巍而从祀。亦
咏归之曾晰则皆见称孔子而犹卑之。是乃溺陈言而昧是非之故也。其亦误矣。且尧舜之道。孔子明之。孔子之道。七十子明之。孔孟之道。程朱明之。程朱之道。各其门人及宋元皇明之诸儒明之。若非孔子则尧舜之道熄矣。若非七十子则孔子之道断矣。若非程朱则孔孟之道废矣。若非门人诸儒则程朱之道塞矣。然则吾道自古及今。赖人显晦者如此。则程朱门人之功。虽有大细。一言一事。皆有关于道理。则孔子复起。尚可取矣。况后人之衣被其德者。当如何哉。若夫汉唐之儒。虽不识道。只研章句。然其圣谟。若无斯人收拾烬馀。则终必泯没无传矣。被发左衽。不疑何卜。今者不须律以大中之法。只许卫道之功。如夫子之许管仲。则亦一道也。中朝必尽罢之者。亦不弘矣。若吾东之祠法。有难晓者。凡吾箕子演九畴之学。始八条之法。今我国家。鸣以礼义之号。丕变蛮貊之俗者。莫非遗泽。则凡我民生。恩若昊天。家家设庙。尚且难报。通都大邑。亦不立祠。是若绥父母之鬼者。可谓无识之甚。而反曰帝王不可立庙。是则国家宗庙。亦皆废之。乃为礼矣。是乃愚夫之妄言。不足诘矣。今不祀箕子。还以谄佛求仙之孤云。独巍巍而从祀。亦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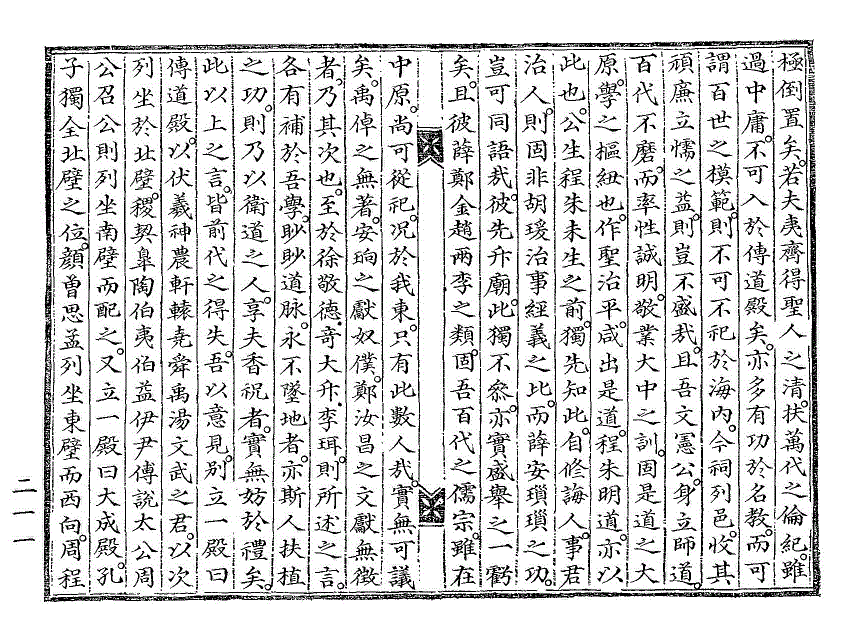 极倒置矣。若夫夷齐得圣人之清。扶万代之伦纪。虽过中庸。不可入于传道殿矣。亦多有功于名教。而可谓百世之模范。则不可不祀于海内。今祠列邑。收其顽廉立懦之益。则岂不盛哉。且吾文宪公。身立师道。百代不磨。而率性诚明。敬业大中之训。固是道之大原。学之枢纽也。作圣治平。咸出是道。程朱明道。亦以此也。公生程朱未生之前。独先知此。自修诲人。事君治人。则固非胡瑗治事经义之比。而薛安琐琐之功。岂可同语哉。彼先升庙。此独不参。亦实盛举之一亏矣。且彼薛郑金赵两李之类。固吾百代之儒宗。虽在中原。尚可从祀。况于我东。只有此数人哉。实无可议矣。禹倬之无著。安珦之献奴仆。郑汝昌之文献无徵者。乃其次也。至于徐敬德,奇大升,李珥。则所述之言。各有补于吾学。眇眇道脉。永不坠地者。亦斯人扶植之功。则乃以卫道之人。享夫香祝者。实无妨于礼矣。此以上之言。皆前代之得失。吾以意见。别立一殿曰传道殿。以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武之君。以次列坐于北壁。稷契皋陶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太公周公召公则列坐南壁而配之。又立一殿曰大成殿。孔子独全北壁之位。颜曾思孟列坐东壁而西向。周程
极倒置矣。若夫夷齐得圣人之清。扶万代之伦纪。虽过中庸。不可入于传道殿矣。亦多有功于名教。而可谓百世之模范。则不可不祀于海内。今祠列邑。收其顽廉立懦之益。则岂不盛哉。且吾文宪公。身立师道。百代不磨。而率性诚明。敬业大中之训。固是道之大原。学之枢纽也。作圣治平。咸出是道。程朱明道。亦以此也。公生程朱未生之前。独先知此。自修诲人。事君治人。则固非胡瑗治事经义之比。而薛安琐琐之功。岂可同语哉。彼先升庙。此独不参。亦实盛举之一亏矣。且彼薛郑金赵两李之类。固吾百代之儒宗。虽在中原。尚可从祀。况于我东。只有此数人哉。实无可议矣。禹倬之无著。安珦之献奴仆。郑汝昌之文献无徵者。乃其次也。至于徐敬德,奇大升,李珥。则所述之言。各有补于吾学。眇眇道脉。永不坠地者。亦斯人扶植之功。则乃以卫道之人。享夫香祝者。实无妨于礼矣。此以上之言。皆前代之得失。吾以意见。别立一殿曰传道殿。以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武之君。以次列坐于北壁。稷契皋陶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太公周公召公则列坐南壁而配之。又立一殿曰大成殿。孔子独全北壁之位。颜曾思孟列坐东壁而西向。周程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2H 页
 张朱列坐西壁而东向。则道统之传益明而孔子集大成之功益显矣。号其东庑曰明道殿。以有卜端闵冉南漆曾仲言之十人为十哲。南向列坐后。东则自冉耕止牧皮之诸人叙之。西则自乐正克止夏钦之诸儒叙之。互相对峙。西配于东。则明理彰道之人。亦有别矣。号其西庑曰卫道殿。以左丘明止欧阳修十四人为主。自刘向止范宁为配则功多而贤。不醇而可取者。亦有辨而不杂也。然雄况九渊守仁之俦则皆是乱吾道者也。虽云有功。不可恕矣。故屏而不言义也。又仿中华创建启圣庙。号曰启道殿。以王季微子叔梁纥位乎北壁。而繇点珦松元定列之。则可得父子彝伦之正矣。我东诸贤则不入文庙。别建闻道殿。祠以箕子。列夷齐而配之。以薛崔郑赵李祠于东庑。以禹止李祠于西庑。则三人之道。益尊东方。明道卫道之人。俱不混矣。乃后列邑之祠。则传道只祀孔子及先儒。明道只祀十哲。闻道只祀三仁五贤。启道亦不降杀而位之。则又得时措之宜矣。位数既定之后。释奠释菜。并行不悖。如闻道殿则四时皆释奠。明道则春秋释奠。冬夏释菜。卫道则只于春秋释奠。而启道则如传道之礼。闻道正殿亦如传
张朱列坐西壁而东向。则道统之传益明而孔子集大成之功益显矣。号其东庑曰明道殿。以有卜端闵冉南漆曾仲言之十人为十哲。南向列坐后。东则自冉耕止牧皮之诸人叙之。西则自乐正克止夏钦之诸儒叙之。互相对峙。西配于东。则明理彰道之人。亦有别矣。号其西庑曰卫道殿。以左丘明止欧阳修十四人为主。自刘向止范宁为配则功多而贤。不醇而可取者。亦有辨而不杂也。然雄况九渊守仁之俦则皆是乱吾道者也。虽云有功。不可恕矣。故屏而不言义也。又仿中华创建启圣庙。号曰启道殿。以王季微子叔梁纥位乎北壁。而繇点珦松元定列之。则可得父子彝伦之正矣。我东诸贤则不入文庙。别建闻道殿。祠以箕子。列夷齐而配之。以薛崔郑赵李祠于东庑。以禹止李祠于西庑。则三人之道。益尊东方。明道卫道之人。俱不混矣。乃后列邑之祠。则传道只祀孔子及先儒。明道只祀十哲。闻道只祀三仁五贤。启道亦不降杀而位之。则又得时措之宜矣。位数既定之后。释奠释菜。并行不悖。如闻道殿则四时皆释奠。明道则春秋释奠。冬夏释菜。卫道则只于春秋释奠。而启道则如传道之礼。闻道正殿亦如传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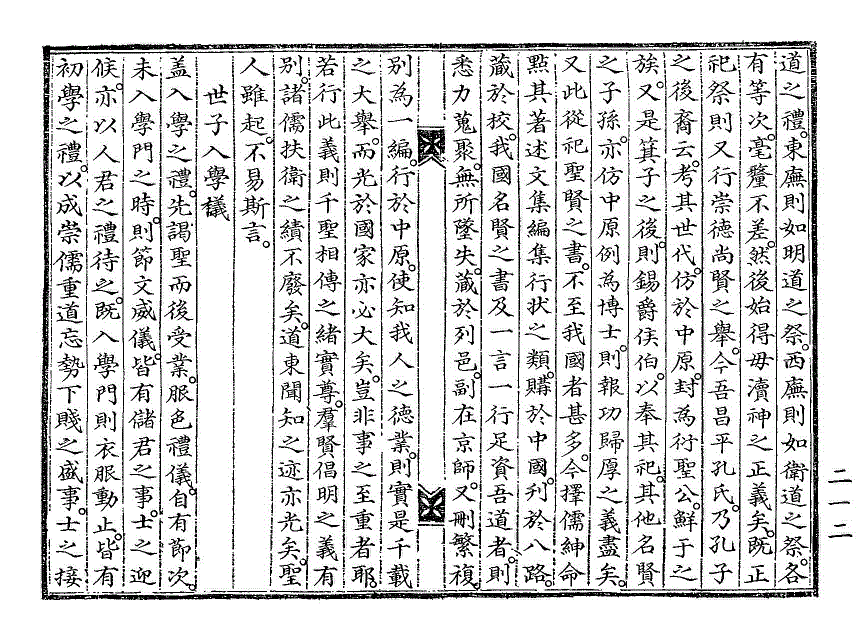 道之礼。东庑则如明道之祭。西庑则如卫道之祭。各有等次。毫釐不差。然后始得毋渎神之正义矣。既正祀祭则又行崇德尚贤之举。今吾昌平孔氏。乃孔子之后裔云。考其世代。仿于中原。封为衍圣公。鲜于之族。又是箕子之后。则锡爵侯伯。以奉其祀。其他名贤之子孙。亦仿中原例为博士。则报功归厚之义尽矣。又此从祀圣贤之书。不至我国者甚多。今择儒绅命点其著述文集编集行状之类。购于中国。刊于八路。藏于校。我国名贤之书及一言一行足资吾道者。则悉力蒐聚。无所坠失。藏于列邑。副在京师。又删繁复。别为一编。行于中原。使知我人之德业。则实是千载之大举。而光于国家亦必大矣。岂非事之至重者耶。若行此义则千圣相传之绪实尊。群贤倡明之义有别。诸儒扶卫之绩不废矣。道东闻知之迹亦光矣。圣人虽起。不易斯言。
道之礼。东庑则如明道之祭。西庑则如卫道之祭。各有等次。毫釐不差。然后始得毋渎神之正义矣。既正祀祭则又行崇德尚贤之举。今吾昌平孔氏。乃孔子之后裔云。考其世代。仿于中原。封为衍圣公。鲜于之族。又是箕子之后。则锡爵侯伯。以奉其祀。其他名贤之子孙。亦仿中原例为博士。则报功归厚之义尽矣。又此从祀圣贤之书。不至我国者甚多。今择儒绅命点其著述文集编集行状之类。购于中国。刊于八路。藏于校。我国名贤之书及一言一行足资吾道者。则悉力蒐聚。无所坠失。藏于列邑。副在京师。又删繁复。别为一编。行于中原。使知我人之德业。则实是千载之大举。而光于国家亦必大矣。岂非事之至重者耶。若行此义则千圣相传之绪实尊。群贤倡明之义有别。诸儒扶卫之绩不废矣。道东闻知之迹亦光矣。圣人虽起。不易斯言。世子入学议
盖入学之礼。先谒圣而后受业。服色礼仪。自有节次。未入学门之时。则节文威仪。皆有储君之事。士之迎候。亦以人君之礼待之。既入学门则衣服动止。皆有初学之礼。以成崇儒重道忘势下贱之盛事。士之接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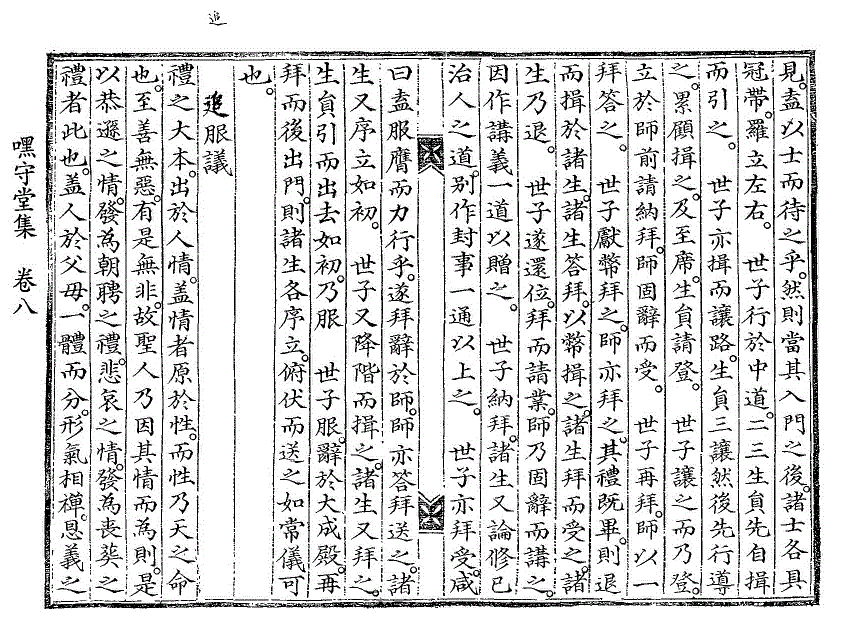 见。盍以士而待之乎。然则当其入门之后。诸士各具冠带。罗立左右。 世子行于中道。二三生员先自揖而引之。 世子亦揖而让路。生员三让然后先行导之。累顾揖之。及至席。生员请登。 世子让之而乃登。立于师前请纳拜。师固辞而受。 世子再拜。师以一拜答之。 世子献币拜之。师亦拜之。其礼既毕。则退而揖于诸生。诸生答拜。以币揖之。诸生拜而受之。诸生乃退。 世子遂还位。拜而请业。师乃固辞而讲之。因作讲义一道以赠之。 世子纳拜。诸生又论修己治人之道。别作封事一通以上之。 世子亦拜受。咸曰盍服膺而力行乎。遂拜辞于师。师亦答拜送之。诸生又序立如初。 世子又降阶而揖之。诸生又拜之。生员引而出去如初。乃服 世子服。辞于大成殿。再拜而后出门。则诸生各序立。俯伏而送之如常仪可也。
见。盍以士而待之乎。然则当其入门之后。诸士各具冠带。罗立左右。 世子行于中道。二三生员先自揖而引之。 世子亦揖而让路。生员三让然后先行导之。累顾揖之。及至席。生员请登。 世子让之而乃登。立于师前请纳拜。师固辞而受。 世子再拜。师以一拜答之。 世子献币拜之。师亦拜之。其礼既毕。则退而揖于诸生。诸生答拜。以币揖之。诸生拜而受之。诸生乃退。 世子遂还位。拜而请业。师乃固辞而讲之。因作讲义一道以赠之。 世子纳拜。诸生又论修己治人之道。别作封事一通以上之。 世子亦拜受。咸曰盍服膺而力行乎。遂拜辞于师。师亦答拜送之。诸生又序立如初。 世子又降阶而揖之。诸生又拜之。生员引而出去如初。乃服 世子服。辞于大成殿。再拜而后出门。则诸生各序立。俯伏而送之如常仪可也。追服议
礼之大本。出于人情。盖情者原于性。而性乃天之命也。至善无恶。有是无非。故圣人乃因其情而为则。是以恭逊之情。发为朝聘之礼。悲哀之情。发为丧葬之礼者此也。盖人于父母。一体而分。形气相禅。恩义之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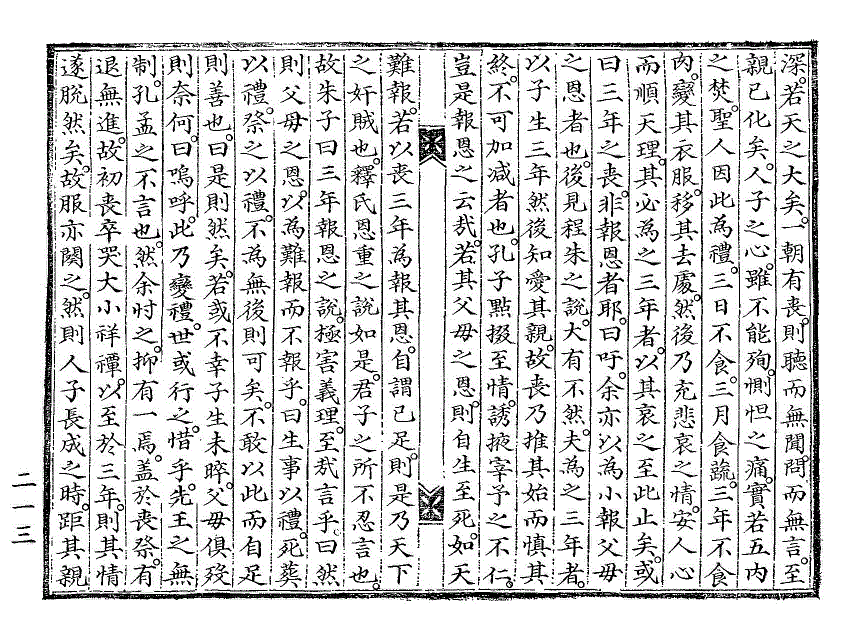 深。若天之大矣。一朝有丧。则听而无闻。问而无言。至亲已化矣。人子之心。虽不能殉。恻怛之痛。实若五内之焚。圣人因此为礼。三日不食。三月食蔬。三年不食肉。变其衣服。移其去处。然后乃充悲哀之情。安人心而顺天理。其必为之三年者。以其哀之至此止矣。或曰三年之丧。非报恩者耶。曰吁。余亦以为小报父母之恩者也。后见程朱之说。大有不然。夫为之三年者。以子生三年然后知爱其亲。故丧乃推其始而慎其终。不可加减者也。孔子点掇至情。诱掖宰予之不仁。岂是报恩之云哉。若其父母之恩。则自生至死。如天难报。若以丧三年为报其恩。自谓已足。则是乃天下之奸贼也。释氏恩重之说如是。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故朱子曰三年报恩之说。极害义理。至哉言乎。曰然则父母之恩。以为难报而不报乎。曰生事以礼。死葬以礼。祭之以礼。不为无后则可矣。不敢以此而自足则善也。曰是则然矣。若或不幸子生未晬。父母俱殁则奈何。曰呜呼。此乃变礼。世或行之。惜乎。先王之无制。孔孟之不言也。然余忖之。抑有一焉。盖于丧祭。有退无进。故初丧卒哭大小祥禫。以至于三年。则其情遂脱然矣。故服亦阕之。然则人子长成之时。距其亲
深。若天之大矣。一朝有丧。则听而无闻。问而无言。至亲已化矣。人子之心。虽不能殉。恻怛之痛。实若五内之焚。圣人因此为礼。三日不食。三月食蔬。三年不食肉。变其衣服。移其去处。然后乃充悲哀之情。安人心而顺天理。其必为之三年者。以其哀之至此止矣。或曰三年之丧。非报恩者耶。曰吁。余亦以为小报父母之恩者也。后见程朱之说。大有不然。夫为之三年者。以子生三年然后知爱其亲。故丧乃推其始而慎其终。不可加减者也。孔子点掇至情。诱掖宰予之不仁。岂是报恩之云哉。若其父母之恩。则自生至死。如天难报。若以丧三年为报其恩。自谓已足。则是乃天下之奸贼也。释氏恩重之说如是。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故朱子曰三年报恩之说。极害义理。至哉言乎。曰然则父母之恩。以为难报而不报乎。曰生事以礼。死葬以礼。祭之以礼。不为无后则可矣。不敢以此而自足则善也。曰是则然矣。若或不幸子生未晬。父母俱殁则奈何。曰呜呼。此乃变礼。世或行之。惜乎。先王之无制。孔孟之不言也。然余忖之。抑有一焉。盖于丧祭。有退无进。故初丧卒哭大小祥禫。以至于三年。则其情遂脱然矣。故服亦阕之。然则人子长成之时。距其亲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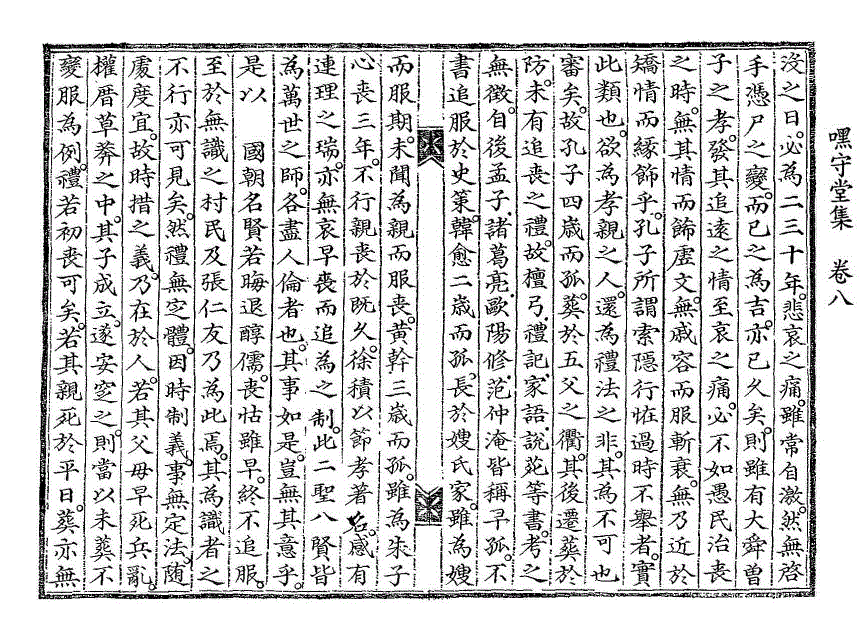 没之日。必为二三十年。悲哀之痛。虽常自激。然无启手凭尸之变。而已之为吉。亦已久矣。则虽有大舜曾子之孝。发其追远之情至哀之痛。必不如愚民治丧之时。无其情而饰虚文。无戚容而服斩衰。无乃近于矫情而缘饰乎。孔子所谓索隐行怪过时不举者。实此类也。欲为孝亲之人。还为礼法之非。其为不可也审矣。故孔子四岁而孤。葬于五父之衢。其后迁葬于防。未有追丧之礼。故檀弓,礼记,家语,说苑等书。考之无徵。自后孟子,诸葛亮,欧阳修,范仲淹皆称早孤。不书追服于史策。韩愈二岁而孤。长于嫂氏家。虽为嫂而服期。未闻为亲而服丧。黄干三岁而孤。虽为朱子心丧三年。不行亲丧于既久。徐积以节孝著名。感有连理之瑞。亦无哀早丧而追为之制。此二圣八贤皆为万世之师。各尽人伦者也。其事如是。岂无其意乎。是以 国朝名贤若晦退醇儒。丧怙虽早。终不追服。至于无识之村民及张仁友乃为此焉。其为识者之不行亦可见矣。然礼无定体。因时制义。事无定法。随处度宜。故时措之义。乃在于人。若其父母早死兵乱。权厝草莽之中。其子成立。遂安窆之。则当以未葬不变服为例。礼若初丧可矣。若其亲死于平日。葬亦无
没之日。必为二三十年。悲哀之痛。虽常自激。然无启手凭尸之变。而已之为吉。亦已久矣。则虽有大舜曾子之孝。发其追远之情至哀之痛。必不如愚民治丧之时。无其情而饰虚文。无戚容而服斩衰。无乃近于矫情而缘饰乎。孔子所谓索隐行怪过时不举者。实此类也。欲为孝亲之人。还为礼法之非。其为不可也审矣。故孔子四岁而孤。葬于五父之衢。其后迁葬于防。未有追丧之礼。故檀弓,礼记,家语,说苑等书。考之无徵。自后孟子,诸葛亮,欧阳修,范仲淹皆称早孤。不书追服于史策。韩愈二岁而孤。长于嫂氏家。虽为嫂而服期。未闻为亲而服丧。黄干三岁而孤。虽为朱子心丧三年。不行亲丧于既久。徐积以节孝著名。感有连理之瑞。亦无哀早丧而追为之制。此二圣八贤皆为万世之师。各尽人伦者也。其事如是。岂无其意乎。是以 国朝名贤若晦退醇儒。丧怙虽早。终不追服。至于无识之村民及张仁友乃为此焉。其为识者之不行亦可见矣。然礼无定体。因时制义。事无定法。随处度宜。故时措之义。乃在于人。若其父母早死兵乱。权厝草莽之中。其子成立。遂安窆之。则当以未葬不变服为例。礼若初丧可矣。若其亲死于平日。葬亦无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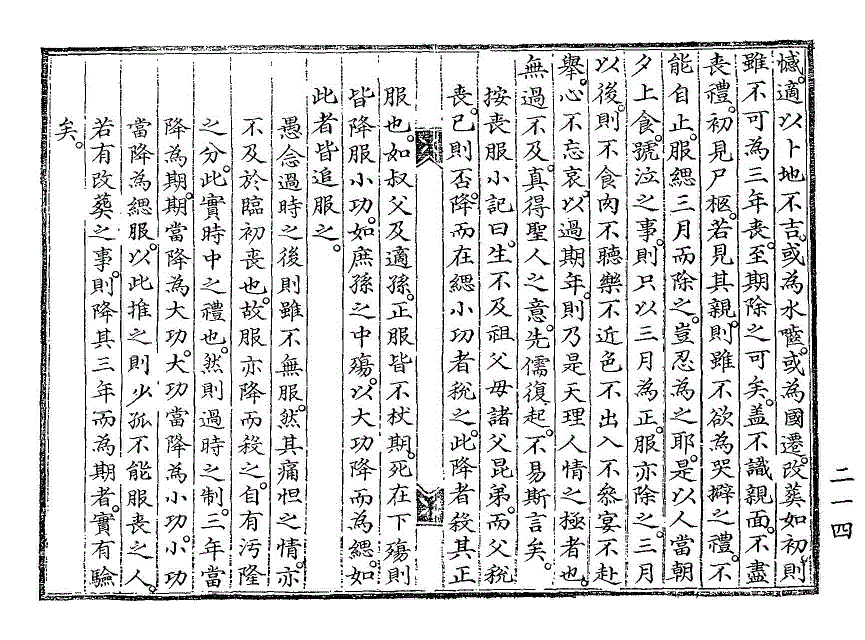 憾。适以卜地不吉。或为水啮。或为国迁。改葬如初。则虽不可为三年丧。至期除之可矣。盖不识亲面。不尽丧礼。初见尸柩。若见其亲。则虽不欲为哭擗之礼。不能自止。服缌三月而除之。岂忍为之耶。是以人当朝夕上食。号泣之事。则只以三月为正。服亦除之。三月以后。则不食肉不听乐不近色不出入不参宴不赴举。心不忘哀。以过期年。则乃是天理人情之极者也。无过不及。真得圣人之意。先儒复起。不易斯言矣。
憾。适以卜地不吉。或为水啮。或为国迁。改葬如初。则虽不可为三年丧。至期除之可矣。盖不识亲面。不尽丧礼。初见尸柩。若见其亲。则虽不欲为哭擗之礼。不能自止。服缌三月而除之。岂忍为之耶。是以人当朝夕上食。号泣之事。则只以三月为正。服亦除之。三月以后。则不食肉不听乐不近色不出入不参宴不赴举。心不忘哀。以过期年。则乃是天理人情之极者也。无过不及。真得圣人之意。先儒复起。不易斯言矣。按丧服小记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降而在缌小功者税之。此降者杀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适孙。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殇则皆降服小功。如庶孙之中殇。以大功降而为缌。如此者皆追服之。
愚念过时之后则虽不无服。然其痛怛之情。亦不及于临初丧也。故服亦降而杀之。自有污隆之分。此实时中之礼也。然则过时之制。三年当降为期。期当降为大功。大功当降为小功。小功当降为缌服。以此推之则少孤不能服丧之人。若有改葬之事。则降其三年而为期者。实有验矣。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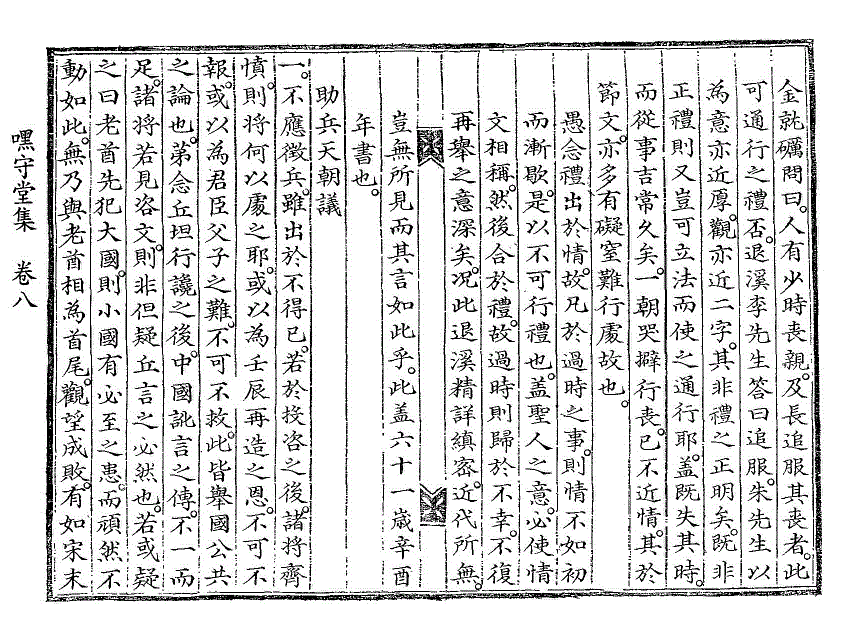 金就砺问曰。人有少时丧亲。及长追服其丧者。此可通行之礼否。退溪李先生答曰追服。朱先生以为意亦近厚。观亦近二字。其非礼之正明矣。既非正礼则又岂可立法而使之通行耶。盖既失其时。而从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丧。已不近情。其于节文。亦多有碍窒难行处故也。
金就砺问曰。人有少时丧亲。及长追服其丧者。此可通行之礼否。退溪李先生答曰追服。朱先生以为意亦近厚。观亦近二字。其非礼之正明矣。既非正礼则又岂可立法而使之通行耶。盖既失其时。而从事吉常久矣。一朝哭擗行丧。已不近情。其于节文。亦多有碍窒难行处故也。愚念礼出于情。故凡于过时之事。则情不如初而渐歇。是以不可行礼也。盖圣人之意。必使情文相称。然后合于礼。故过时则归于不幸。不复再举之意深矣。况此退溪精详缜密。近代所无。岂无所见而其言如此乎。此盖六十一岁辛酉年书也。
助兵天朝议
一。不应徵兵。虽出于不得已。若于投咨之后。诸将齐愤。则将何以处之耶。或以为壬辰再造之恩。不可不报。或以为君臣父子之难。不可不救。此皆举国公共之论也。第念丘坦行谗之后。中国讹言之传。不一而足。诸将若见咨文。则非但疑丘言之必然也。若或疑之曰老酋先犯大国。则小国有必至之患。而顽然不动如此。无乃与老酋相为首尾。观望成败。有如宋末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5L 页
 高丽臣伏契丹之事耶云。则我国将以何辞自立于天地乎。壬辰倭寇之惨。万古所无。而不通倭贼。鬼神亦知。丁应泰尚以招倭犯 上国。题奏天子。况今形势则大异于前。而我国境连老酋。中国所详知。若于此时。丘坦构出不测之言。一如丁应泰。则我国踪迹败露。万无自解之路矣。思之至此。不知所以处置者。良可寒心矣。
高丽臣伏契丹之事耶云。则我国将以何辞自立于天地乎。壬辰倭寇之惨。万古所无。而不通倭贼。鬼神亦知。丁应泰尚以招倭犯 上国。题奏天子。况今形势则大异于前。而我国境连老酋。中国所详知。若于此时。丘坦构出不测之言。一如丁应泰。则我国踪迹败露。万无自解之路矣。思之至此。不知所以处置者。良可寒心矣。一。天朝敕谕之来不来。有不可论。盖天朝之制。不如我国之规。阁老自制批辞而进之。则皇上只书是字而下之。称为奉圣旨是而已。此则经理军门及诸御史一题本驰奏之日。即敕谕来到之时也。敕谕既到则难拒徵兵。中国将差星夜督军。而我国亦不免刻日促送。则骚扰之端。民心之动。必有甚于前期号令之事矣。为国计者。莫如预整军兵。以待敕谕而即发矣。然则一以无后期之忧。一以无人心危急之弊矣。一或人以为老贼若不胜中国。则必不能窥我国。此则不然。此贼非如草窃之比。每有射天之志。犯于上国不能抵当。则必有纵兵移怒。欲除中国之藩屏矣。昔红巾贼亦不得志于中国。故横奔到此。若以两虎共斗。势不俱生者比之。大不相近。为国虑远。则所当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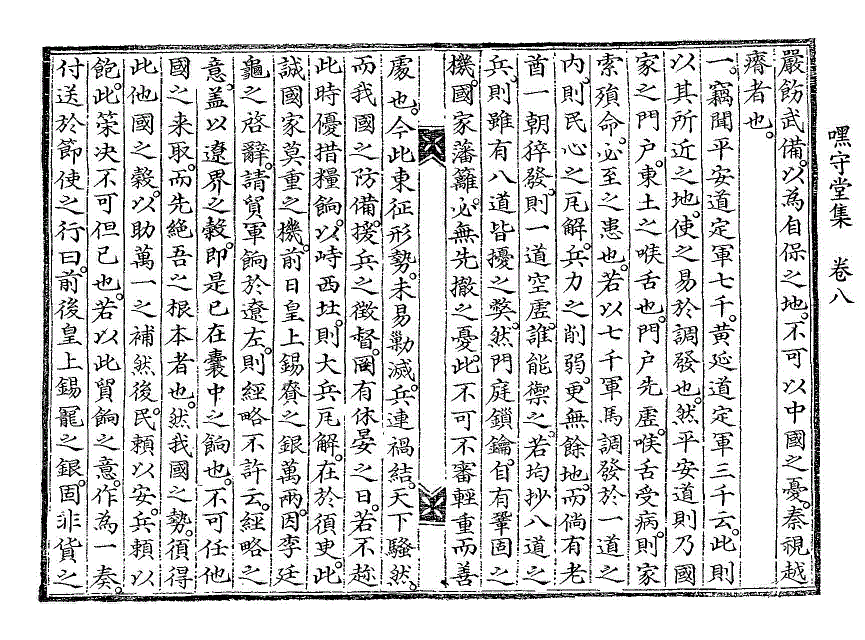 严饬武备。以为自保之地。不可以中国之忧。秦视越瘠者也。
严饬武备。以为自保之地。不可以中国之忧。秦视越瘠者也。一。窃闻平安道定军七千。黄延道定军三千云。此则以其所近之地。使之易于调发也。然平安道则乃国家之门户。东土之喉舌也。门户先虚。喉舌受病。则家索殒命。必至之患也。若以七千军马调发于一道之内。则民心之瓦解。兵力之削弱。更无馀地。而倘有老酋一朝猝发。则一道空虚。谁能御之。若均抄八道之兵。则虽有八道皆扰之弊。然门庭锁钥。自有巩固之机。国家藩篱。必无先撤之忧。此不可不审轻重而善处也。今此东征形势。未易剿灭。兵连祸结。天下骚然。而我国之防备。援兵之徵督。罔有休晏之日。若不趁此时优措粮饷。以峙西北。则大兵瓦解。在于须臾。此诚国家莫重之机。前日皇上锡赉之银万两。因李廷龟之启辞。请贸军饷于辽左。则经略不许云。经略之意。盖以辽界之谷。即是已在囊中之饷也。不可任他国之来取。而先绝吾之根本者也。然我国之势。须得此他国之谷。以助万一之补然后。民赖以安。兵赖以饱。此策决不可但已也。若以此贸饷之意。作为一奏。付送于节使之行曰。前后皇上锡宠之银。固非货之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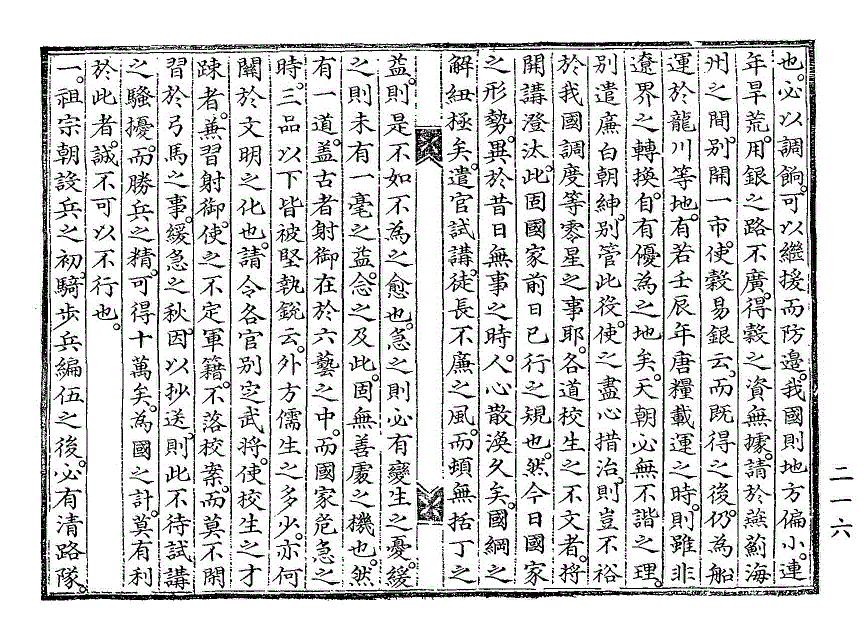 也。必以调饷。可以继援而防边。我国则地方偏小。连年旱荒。用银之路不广。得谷之资无据。请于燕蓟海州之间。别开一市。使谷易银云。而既得之后。仍为船运于龙川等地。有若壬辰年唐粮载运之时。则虽非辽界之转换。自有优为之地矣。天朝必无不谐之理。别遣廉白朝绅。别管此役。使之尽心措治。则岂不裕于我国调度等零星之事耶。各道校生之不文者。将开讲澄汰。此固国家前日已行之规也。然今日国家之形势。异于昔日无事之时。人心散涣久矣。国纲之解纽极矣。遣官试讲。徒长不廉之风。而顿无括丁之益。则是不如不为之愈也。急之则必有变生之忧。缓之则未有一毫之益。念之及此。固无善处之机也。然有一道。盖古者射御在于六艺之中。而国家危急之时。三品以下皆被坚执锐云。外方儒生之多少。亦何关于文明之化也。请令各官别定武将。使校生之才疏者。兼习射御。使之不定军籍。不落校案。而莫不闲习于弓马之事。缓急之秋。因以抄送。则此不待试讲之骚扰。而胜兵之精。可得十万矣。为国之计。莫有利于此者。诚不可以不行也。
也。必以调饷。可以继援而防边。我国则地方偏小。连年旱荒。用银之路不广。得谷之资无据。请于燕蓟海州之间。别开一市。使谷易银云。而既得之后。仍为船运于龙川等地。有若壬辰年唐粮载运之时。则虽非辽界之转换。自有优为之地矣。天朝必无不谐之理。别遣廉白朝绅。别管此役。使之尽心措治。则岂不裕于我国调度等零星之事耶。各道校生之不文者。将开讲澄汰。此固国家前日已行之规也。然今日国家之形势。异于昔日无事之时。人心散涣久矣。国纲之解纽极矣。遣官试讲。徒长不廉之风。而顿无括丁之益。则是不如不为之愈也。急之则必有变生之忧。缓之则未有一毫之益。念之及此。固无善处之机也。然有一道。盖古者射御在于六艺之中。而国家危急之时。三品以下皆被坚执锐云。外方儒生之多少。亦何关于文明之化也。请令各官别定武将。使校生之才疏者。兼习射御。使之不定军籍。不落校案。而莫不闲习于弓马之事。缓急之秋。因以抄送。则此不待试讲之骚扰。而胜兵之精。可得十万矣。为国之计。莫有利于此者。诚不可以不行也。一。祖宗朝设兵之初。骑步兵编伍之后。必有清路队。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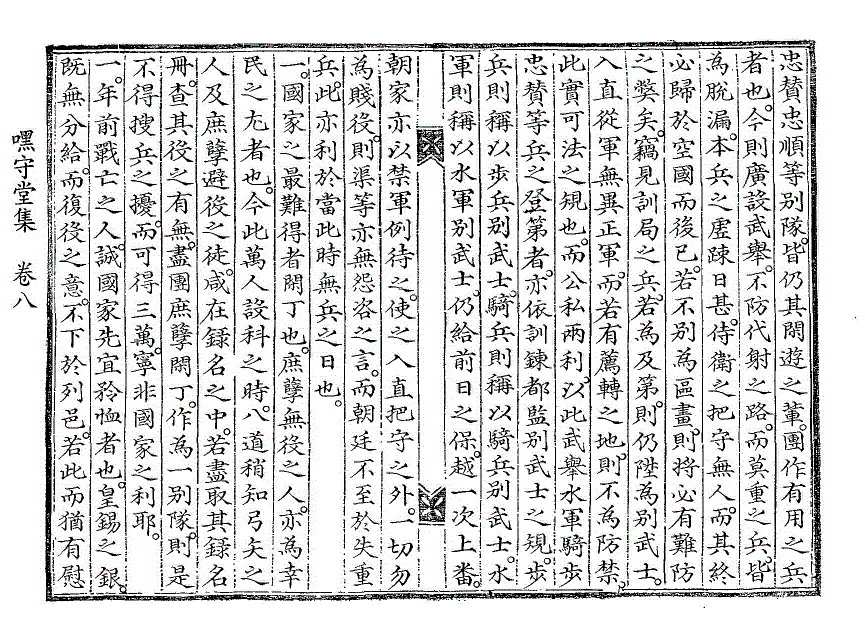 忠赞忠顺等别队。皆仍其闲游之辈。团作有用之兵者也。今则广设武举。不防代射之路。而莫重之兵。皆为脱漏。本兵之虚疏日甚。侍卫之把守无人。而其终必归于空国而后已。若不别为区画。则将必有难防之弊矣。窃见训局之兵。若为及第。则仍升为别武士。入直从军无异正军。而若有荐转之地。则不为防禁。此实可法之规也。而公私两利。以此武举水军骑步忠赞等兵之登第者。亦依训鍊都监别武士之规。步兵则称以步兵别武士。骑兵则称以骑兵别武士。水军则称以水军别武士。仍给前日之保。越一次上番。朝家亦以禁军例待之。使之入直把守之外。一切勿为贱役。则渠等亦无怨咨之言。而朝廷不至于失重兵。此亦利于当此时无兵之日也。
忠赞忠顺等别队。皆仍其闲游之辈。团作有用之兵者也。今则广设武举。不防代射之路。而莫重之兵。皆为脱漏。本兵之虚疏日甚。侍卫之把守无人。而其终必归于空国而后已。若不别为区画。则将必有难防之弊矣。窃见训局之兵。若为及第。则仍升为别武士。入直从军无异正军。而若有荐转之地。则不为防禁。此实可法之规也。而公私两利。以此武举水军骑步忠赞等兵之登第者。亦依训鍊都监别武士之规。步兵则称以步兵别武士。骑兵则称以骑兵别武士。水军则称以水军别武士。仍给前日之保。越一次上番。朝家亦以禁军例待之。使之入直把守之外。一切勿为贱役。则渠等亦无怨咨之言。而朝廷不至于失重兵。此亦利于当此时无兵之日也。一。国家之最难得者闲丁也。庶孽无役之人。亦为幸民之尤者也。今此万人设科之时。八道稍知弓矢之人及庶孽避役之徒。咸在录名之中。若尽取其录名册。查其役之有无。尽团庶孽闲丁。作为一别队。则是不得搜兵之扰。而可得三万。宁非国家之利耶。
一。年前战亡之人。诚国家先宜矜恤者也。皇锡之银。既无分给。而复役之意。不下于列邑。若此而犹有慰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7L 页
 民死长之望。则岂不左耶。伏望别遣巡抚御史。特下哀痛之教。有父母者以空名告身分给之。有子支者复其役。奴隶则免其贱。特行优恤之典。民有庶几亲上之心矣。
民死长之望。则岂不左耶。伏望别遣巡抚御史。特下哀痛之教。有父母者以空名告身分给之。有子支者复其役。奴隶则免其贱。特行优恤之典。民有庶几亲上之心矣。流民安接议
人各定居。自有安土之乐。民之至愿。流离失巢者。岂人之本心哉。前日守令之贪剥。方伯之暴虐。百役猬起。酷刑狼噬。使百姓不得一日之安。不得已弃其良田。远接他邑。以为避水火之计。此入作之日多民役之日重者也。念之可为哀矜矣。不可不及时施仁政。以安集为先务也。今宣令于各官。使流亡之人。各还本土。身役之逋欠者除之。田宅之已卖者还畀之。限一年复身役。勿任以事。不愿还归者。则因为著籍于所居之地。去者留者。并为成册。上于帅府。以为凭阅之据。则安接之策。莫大于此也。各官守令。各面坊里中。择定有识人为里有司。专掌入作。前日入来某处某人。逐一开报本官。本官转报帅府。以考其实。万一守令容私不以实报。里有司容私有所脱漏。则五名以上罢黜。十名以上充军。里有司定配。则隐漏奸民。不敢逃其迹矣。入作等万无自为一村之理。必来接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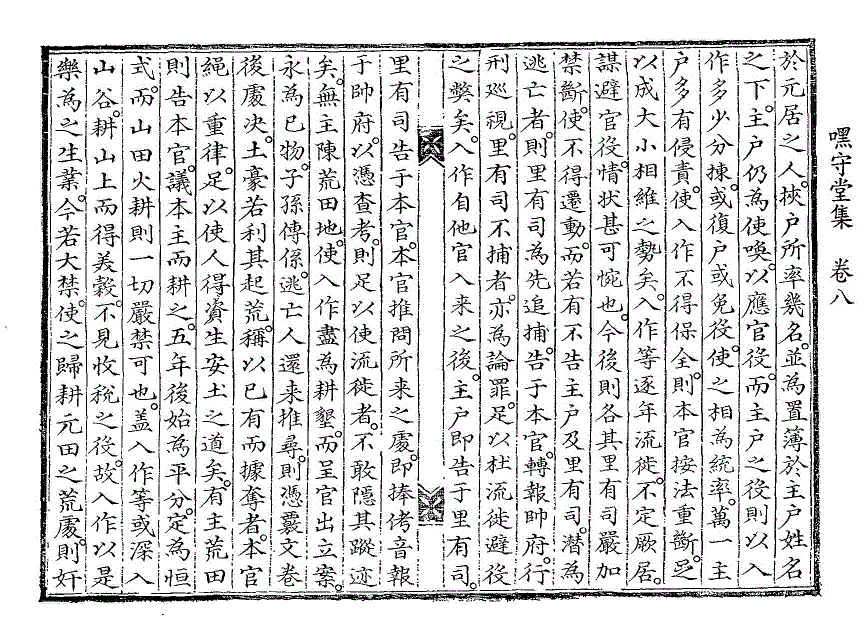 于元居之人。挟户所率几名。并为置簿于主户姓名之下。主户仍为使唤。以应官役。而主户之役则以入作多少分拣。或复户或免役。使之相为统率。万一主户多有侵责。使入作不得保全。则本官按法重断。足以成大小相维之势矣。入作等逐年流徙。不定厥居。谋避官役。情状甚可惋也。今后则各其里有司严加禁断。使不得迁动。而若有不告主户及里有司。潜为逃亡者。则里有司为先追捕。告于本官。转报帅府。行刑巡视。里有司不捕者。亦为论罪。足以杜流徙避役之弊矣。入作自他官入来之后。主户即告于里有司。里有司告于本官。本官推问所来之处。即捧侤音报于帅府。以凭查考。则足以使流徙者。不敢隐其踪迹矣。无主陈荒田地。使入作尽为耕垦。而呈官出立案。永为己物。子孙传系。逃亡人还来推寻。则凭覈文卷后处决。土豪若利其起荒。称以己有而据夺者。本官绳以重律。足以使人得资生安土之道矣。有主荒田则告本官。议本主而耕之。五年后始为平分。定为恒式。而山田火耕则一切严禁可也。盖入作等或深入山谷。耕山上而得美谷。不见收税之役。故入作以是乐为之生业。今若大禁。使之归耕元田之荒处。则奸
于元居之人。挟户所率几名。并为置簿于主户姓名之下。主户仍为使唤。以应官役。而主户之役则以入作多少分拣。或复户或免役。使之相为统率。万一主户多有侵责。使入作不得保全。则本官按法重断。足以成大小相维之势矣。入作等逐年流徙。不定厥居。谋避官役。情状甚可惋也。今后则各其里有司严加禁断。使不得迁动。而若有不告主户及里有司。潜为逃亡者。则里有司为先追捕。告于本官。转报帅府。行刑巡视。里有司不捕者。亦为论罪。足以杜流徙避役之弊矣。入作自他官入来之后。主户即告于里有司。里有司告于本官。本官推问所来之处。即捧侤音报于帅府。以凭查考。则足以使流徙者。不敢隐其踪迹矣。无主陈荒田地。使入作尽为耕垦。而呈官出立案。永为己物。子孙传系。逃亡人还来推寻。则凭覈文卷后处决。土豪若利其起荒。称以己有而据夺者。本官绳以重律。足以使人得资生安土之道矣。有主荒田则告本官。议本主而耕之。五年后始为平分。定为恒式。而山田火耕则一切严禁可也。盖入作等或深入山谷。耕山上而得美谷。不见收税之役。故入作以是乐为之生业。今若大禁。使之归耕元田之荒处。则奸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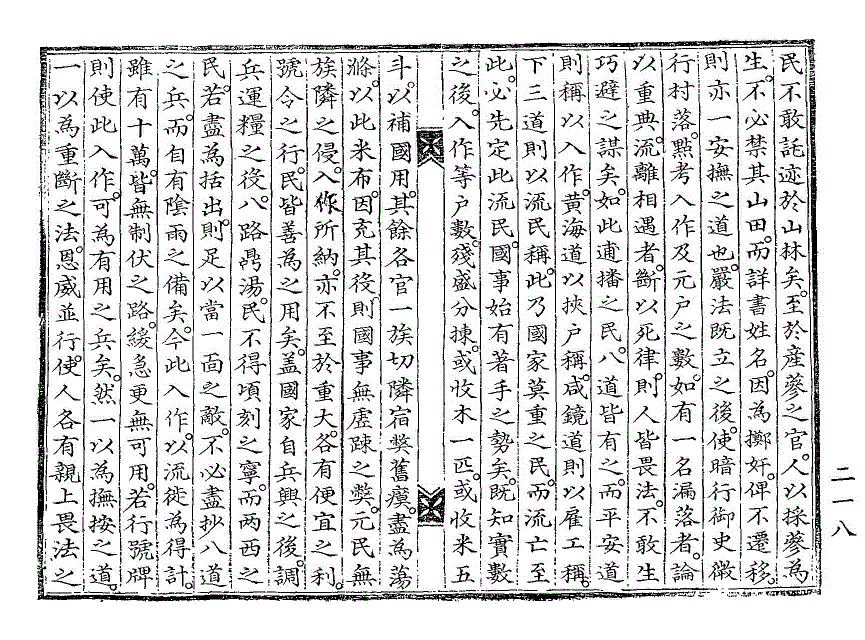 民不敢托迹于山林矣。至于产蔘之官。人以采蔘为生。不必禁其山田。而详书姓名。因为掷奸。俾不迁移。则亦一安抚之道也。严法既立之后。使暗行御史微行村落。点考入作及元户之数。如有一名漏落者。论以重典。流离相遇者。断以死律。则人皆畏法。不敢生巧避之谋矣。如此逋播之民。八道皆有之。而平安道则称以入作。黄海道以挟户称。咸镜道则以雇工称。下三道则以流民称。此乃国家莫重之民。而流亡至此。必先定此流民。国事始有著手之势矣。既知实数之后。入作等户数。残盛分拣。或收木一匹。或收米五斗。以补国用。其馀各官一族切邻宿弊旧瘼。尽为荡涤。以此米布。因充其役。则国事无虚疏之弊。元民无族邻之侵。入作所纳。亦不至于重大。各有便宜之利。号令之行。民皆善为之用矣。盖国家自兵兴之后。调兵运粮之役。八路鼎汤。民不得顷刻之宁。而两西之民。若尽为括出。则足以当一面之敌。不必尽抄八道之兵。而自有阴雨之备矣。今此入作。以流徙为得计。虽有十万。皆无制伏之路。缓急更无可用。若行号牌则使此入作。可为有用之兵矣。然一以为抚按之道。一以为重断之法。恩威并行。使人各有亲上畏法之
民不敢托迹于山林矣。至于产蔘之官。人以采蔘为生。不必禁其山田。而详书姓名。因为掷奸。俾不迁移。则亦一安抚之道也。严法既立之后。使暗行御史微行村落。点考入作及元户之数。如有一名漏落者。论以重典。流离相遇者。断以死律。则人皆畏法。不敢生巧避之谋矣。如此逋播之民。八道皆有之。而平安道则称以入作。黄海道以挟户称。咸镜道则以雇工称。下三道则以流民称。此乃国家莫重之民。而流亡至此。必先定此流民。国事始有著手之势矣。既知实数之后。入作等户数。残盛分拣。或收木一匹。或收米五斗。以补国用。其馀各官一族切邻宿弊旧瘼。尽为荡涤。以此米布。因充其役。则国事无虚疏之弊。元民无族邻之侵。入作所纳。亦不至于重大。各有便宜之利。号令之行。民皆善为之用矣。盖国家自兵兴之后。调兵运粮之役。八路鼎汤。民不得顷刻之宁。而两西之民。若尽为括出。则足以当一面之敌。不必尽抄八道之兵。而自有阴雨之备矣。今此入作。以流徙为得计。虽有十万。皆无制伏之路。缓急更无可用。若行号牌则使此入作。可为有用之兵矣。然一以为抚按之道。一以为重断之法。恩威并行。使人各有亲上畏法之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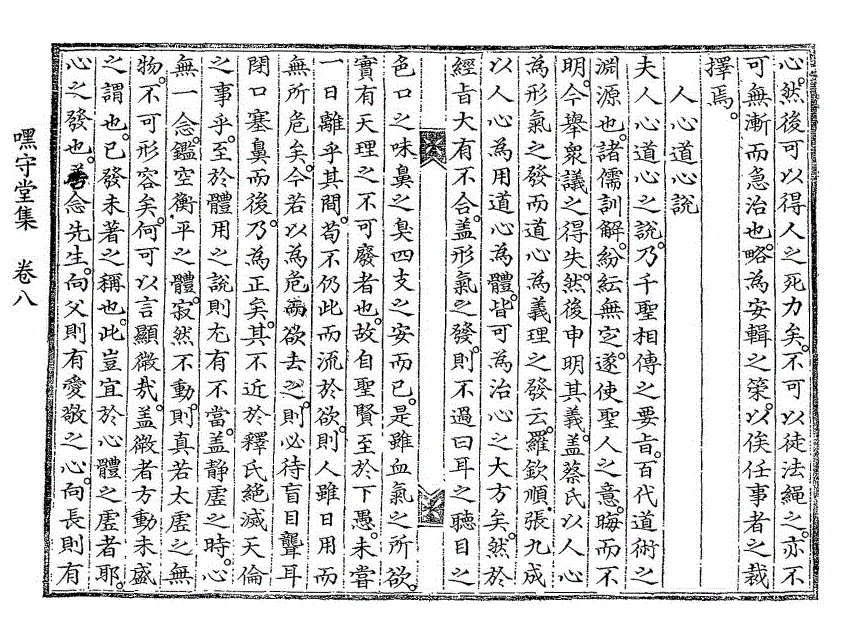 心。然后可以得人之死力矣。不可以徒法绳之。亦不可无渐而急治也。略为安辑之策。以俟任事者之裁择焉。
心。然后可以得人之死力矣。不可以徒法绳之。亦不可无渐而急治也。略为安辑之策。以俟任事者之裁择焉。人心道心说
夫人心道心之说。乃千圣相传之要旨。百代道术之渊源也。诸儒训解。纷纭无定。遂使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今举众议之得失。然后申明其义。盖蔡氏以人心为形气之发而道心为义理之发云。罗钦顺,张九成以人心为用道心为体。皆可为治心之大方矣。然于经旨大有不合。盖形气之发。则不过曰耳之听目之色口之味鼻之臭四支之安而已。是虽血气之所欲。实有天理之不可废者也。故自圣贤至于下愚。未尝一日离乎其间。苟不仍此而流于欲。则人虽日用而无所危矣。今若以为危而欲去之。则必待盲目聋耳闭口塞鼻而后。乃为正矣。其不近于释氏绝灭天伦之事乎。至于体用之说则尤有不当。盖静虚之时。心无一念。鉴空衡平之体。寂然不动。则真若太虚之无物。不可形容矣。何可以言显微哉。盖微者方动未盛之谓也。已发未著之称也。此岂宜于心体之虚者耶。心之发也。善念先生。向父则有爱敬之心。向长则有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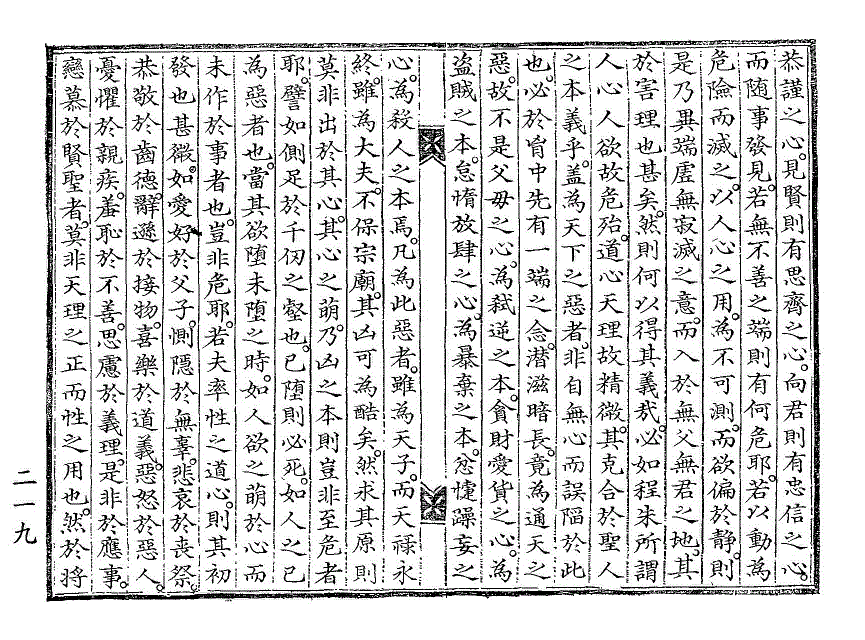 恭谨之心。见贤则有思齐之心。向君则有忠信之心。而随事发见。若无不善之端则有何危耶。若以动为危险而灭之。以人心之用。为不可测。而欲偏于静。则是乃异端虚无寂灭之意。而入于无父无君之地。其于害理也甚矣。然则何以得其义哉。必如程朱所谓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其克合于圣人之本义乎。盖为天下之恶者。非自无心而误陷于此也。必于胸中先有一端之念。潜滋暗长。竟为通天之恶。故不是父母之心。为弑逆之本。贪财爱货之心。为盗贼之本。怠惰放肆之心。为暴弃之本。忿懥躁妄之心。为杀人之本焉。凡为此恶者。虽为天子。而天禄永终。虽为大夫。不保宗庙。其凶可为酷矣。然求其原则莫非出于其心。其心之萌。乃凶之本则岂非至危者耶。譬如侧足于千仞之壑也。已堕则必死。如人之已为恶者也。当其欲堕未堕之时。如人欲之萌于心而未作于事者也。岂非危耶。若夫率性之道心。则其初发也甚微。如爱好于父子。恻隐于无辜。悲哀于丧祭。恭敬于齿德。辞逊于接物。喜乐于道义。恶怒于恶人。忧惧于亲疾。羞耻于不善。思虑于义理。是非于应事。恋慕于贤圣者。莫非天理之正而性之用也。然于将
恭谨之心。见贤则有思齐之心。向君则有忠信之心。而随事发见。若无不善之端则有何危耶。若以动为危险而灭之。以人心之用。为不可测。而欲偏于静。则是乃异端虚无寂灭之意。而入于无父无君之地。其于害理也甚矣。然则何以得其义哉。必如程朱所谓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其克合于圣人之本义乎。盖为天下之恶者。非自无心而误陷于此也。必于胸中先有一端之念。潜滋暗长。竟为通天之恶。故不是父母之心。为弑逆之本。贪财爱货之心。为盗贼之本。怠惰放肆之心。为暴弃之本。忿懥躁妄之心。为杀人之本焉。凡为此恶者。虽为天子。而天禄永终。虽为大夫。不保宗庙。其凶可为酷矣。然求其原则莫非出于其心。其心之萌。乃凶之本则岂非至危者耶。譬如侧足于千仞之壑也。已堕则必死。如人之已为恶者也。当其欲堕未堕之时。如人欲之萌于心而未作于事者也。岂非危耶。若夫率性之道心。则其初发也甚微。如爱好于父子。恻隐于无辜。悲哀于丧祭。恭敬于齿德。辞逊于接物。喜乐于道义。恶怒于恶人。忧惧于亲疾。羞耻于不善。思虑于义理。是非于应事。恋慕于贤圣者。莫非天理之正而性之用也。然于将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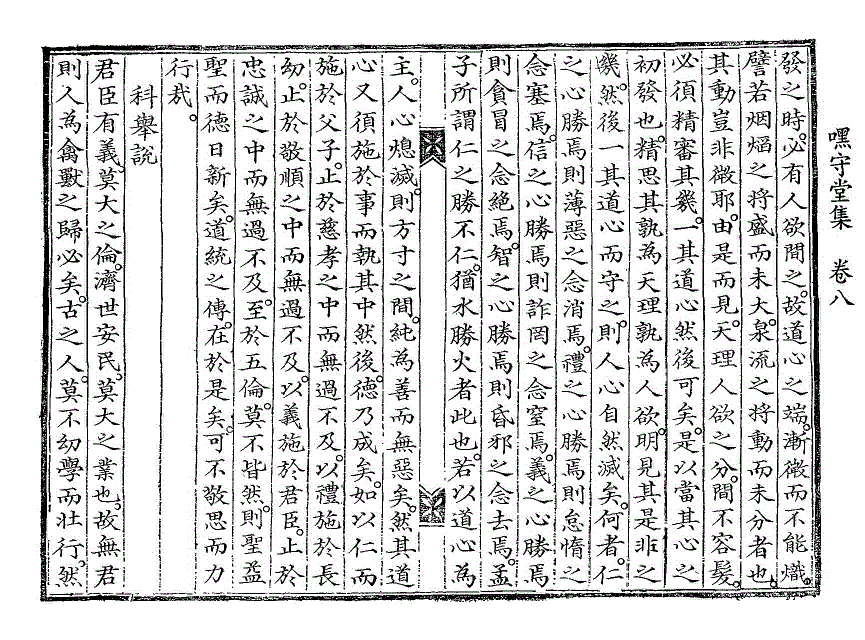 发之时。必有人欲间之。故道心之端。渐微而不能炽。譬若烟焰之将盛而未大。泉流之将动而未分者也。其动岂非微耶。由是而见。天理人欲之分。间不容发。必须精审其几。一其道心然后可矣。是以当其心之初发也。精思其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明见其是非之几。然后一其道心而守之。则人心自然灭矣。何者。仁之心胜焉则薄恶之念消焉。礼之心胜焉则怠惰之念塞焉。信之心胜焉则诈罔之念窒焉。义之心胜焉则贪冒之念绝焉。智之心胜焉则昏邪之念去焉。孟子所谓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者此也。若以道心为主。人心熄灭。则方寸之间。纯为善而无恶矣。然其道心又须施于事而执其中然后。德乃成矣。如以仁而施于父子。止于慈孝之中而无过不及。以礼施于长幼。止于敬顺之中而无过不及。以义施于君臣。止于忠诚之中而无过不及。至于五伦。莫不皆然。则圣益圣而德日新矣。道统之传。在于是矣。可不敬思而力行哉。
发之时。必有人欲间之。故道心之端。渐微而不能炽。譬若烟焰之将盛而未大。泉流之将动而未分者也。其动岂非微耶。由是而见。天理人欲之分。间不容发。必须精审其几。一其道心然后可矣。是以当其心之初发也。精思其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明见其是非之几。然后一其道心而守之。则人心自然灭矣。何者。仁之心胜焉则薄恶之念消焉。礼之心胜焉则怠惰之念塞焉。信之心胜焉则诈罔之念窒焉。义之心胜焉则贪冒之念绝焉。智之心胜焉则昏邪之念去焉。孟子所谓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者此也。若以道心为主。人心熄灭。则方寸之间。纯为善而无恶矣。然其道心又须施于事而执其中然后。德乃成矣。如以仁而施于父子。止于慈孝之中而无过不及。以礼施于长幼。止于敬顺之中而无过不及。以义施于君臣。止于忠诚之中而无过不及。至于五伦。莫不皆然。则圣益圣而德日新矣。道统之传。在于是矣。可不敬思而力行哉。科举说
君臣有义。莫大之伦。济世安民。莫大之业也。故无君则人为禽兽之归必矣。古之人。莫不幼学而壮行。然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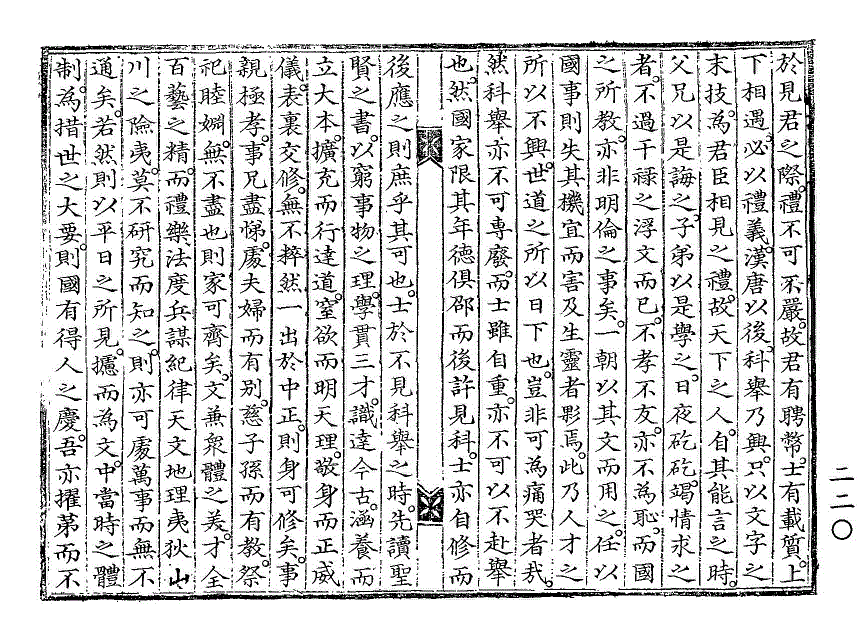 于见君之际。礼不可不严。故君有聘币。士有载质。上下相遇。必以礼义。汉唐以后。科举乃兴。只以文字之末技。为君臣相见之礼。故天下之人。自其能言之时。父兄以是诲之。子弟以是学之。日夜矻矻。竭情求之者。不过干禄之浮文而已。不孝不友。亦不为耻。而国之所教。亦非明伦之事矣。一朝以其文而用之。任以国事则失其机宜而害及生灵者夥焉。此乃人才之所以不兴。世道之所以日下也。岂非可为痛哭者哉。然科举亦不可专废。而士虽自重。亦不可以不赴举也。然国家限其年德俱卲而后许见科。士亦自修而后应之则庶乎其可也。士于不见科举之时。先读圣贤之书。以穷事物之理。学贯三才。识达今古。涵养而立大本。扩充而行达道。窒欲而明天理。敬身而正威仪。表里交修。无不粹然一出于中正。则身可修矣。事亲极孝。事兄尽悌。处夫妇而有别。慈子孙而有教。祭祀睦姻。无不尽也则家可齐矣。文兼众体之美。才全百艺之精。而礼乐法度兵谋纪律天文地理夷狄山川之险夷。莫不研究而知之。则亦可处万事而无不通矣。若然则以平日之所见。摅而为文。中当时之体制。为措世之大要。则国有得人之庆。吾亦擢第而不
于见君之际。礼不可不严。故君有聘币。士有载质。上下相遇。必以礼义。汉唐以后。科举乃兴。只以文字之末技。为君臣相见之礼。故天下之人。自其能言之时。父兄以是诲之。子弟以是学之。日夜矻矻。竭情求之者。不过干禄之浮文而已。不孝不友。亦不为耻。而国之所教。亦非明伦之事矣。一朝以其文而用之。任以国事则失其机宜而害及生灵者夥焉。此乃人才之所以不兴。世道之所以日下也。岂非可为痛哭者哉。然科举亦不可专废。而士虽自重。亦不可以不赴举也。然国家限其年德俱卲而后许见科。士亦自修而后应之则庶乎其可也。士于不见科举之时。先读圣贤之书。以穷事物之理。学贯三才。识达今古。涵养而立大本。扩充而行达道。窒欲而明天理。敬身而正威仪。表里交修。无不粹然一出于中正。则身可修矣。事亲极孝。事兄尽悌。处夫妇而有别。慈子孙而有教。祭祀睦姻。无不尽也则家可齐矣。文兼众体之美。才全百艺之精。而礼乐法度兵谋纪律天文地理夷狄山川之险夷。莫不研究而知之。则亦可处万事而无不通矣。若然则以平日之所见。摅而为文。中当时之体制。为措世之大要。则国有得人之庆。吾亦擢第而不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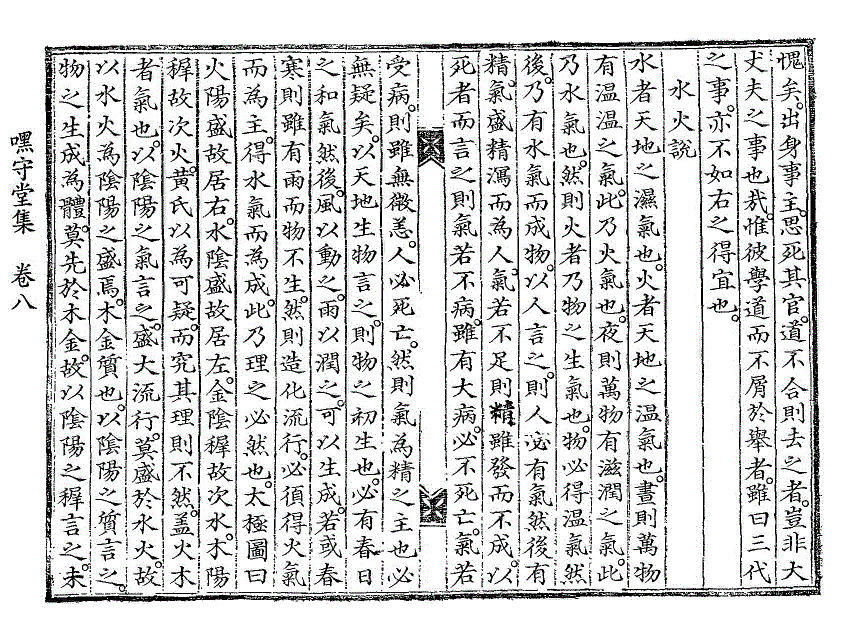 愧矣。出身事主。思死其官。道不合则去之者。岂非大丈夫之事也哉。惟彼学道而不屑于举者。虽曰三代之事。亦不如右之得宜也。
愧矣。出身事主。思死其官。道不合则去之者。岂非大丈夫之事也哉。惟彼学道而不屑于举者。虽曰三代之事。亦不如右之得宜也。水火说
水者天地之湿气也。火者天地之温气也。昼则万物有温温之气。此乃火气也。夜则万物有滋润之气。此乃水气也。然则火者乃物之生气也。物必得温气然后。乃有水气而成物。以人言之。则人必有气然后有精。气盛精泻而为人。气若不足则精虽发而不成。以死者而言之则气若不病。虽有大病。必不死亡。气若受病。则虽无微恙。人必死亡。然则气为精之主也必无疑矣。以天地生物言之。则物之初生也。必有春日之和气然后。风以动之。雨以润之。可以生成。若或春寒则虽有雨而物不生。然则造化流行。必须得火气而为主。得水气而为成。此乃理之必然也。太极图曰火阳盛故居右。水阴盛故居左。金阴𥠧故次水。木阳𥠧故次火。黄氏以为可疑。而究其理则不然。盖火木者气也。以阴阳之气言之。盛大流行。莫盛于水火。故以水火为阴阳之盛焉。木金质也。以阴阳之质言之。物之生成为体。莫先于木金。故以阴阳之𥠧言之。未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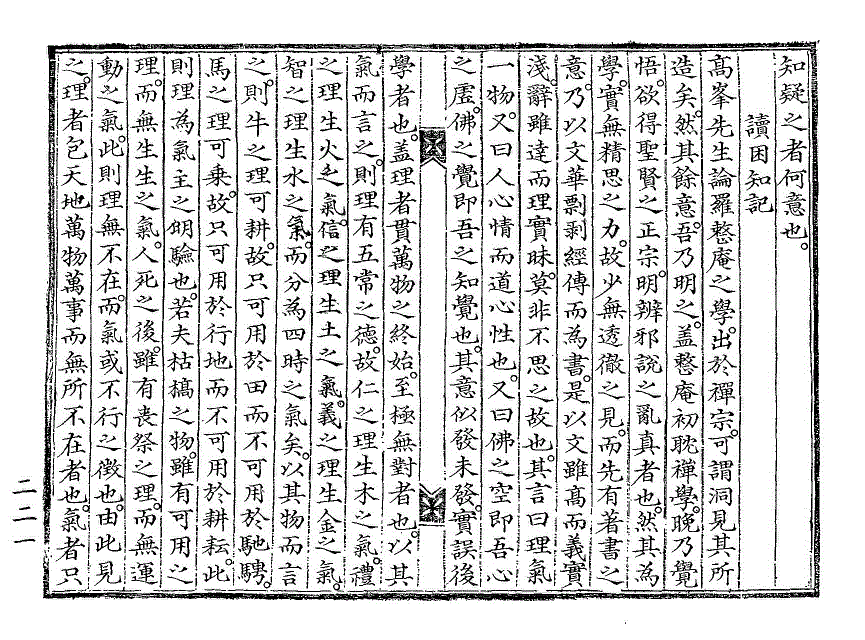 知疑之者何意也。
知疑之者何意也。读困知记
高峰先生论罗整庵之学。出于禅宗。可谓洞见其所造矣。然其馀意。吾乃明之。盖整庵初耽禅学。晚乃觉悟。欲得圣贤之正宗。明辨邪说之乱真者也。然其为学。实无精思之力。故少无透彻之见。而先有著书之意。乃以文华剽剥经传而为书。是以文虽高而义实浅。辞虽达而理实昧。莫非不思之故也。其言曰理气一物。又曰人心情而道心性也。又曰佛之空即吾心之虚。佛之觉即吾之知觉也。其意似发未发。实误后学者也。盖理者贯万物之终始。至极无对者也。以其气而言之。则理有五常之德。故仁之理生木之气。礼之理生火之气。信之理生土之气。义之理生金之气。智之理生水之气。而分为四时之气矣。以其物而言之。则牛之理可耕。故只可用于田而不可用于驰骋。马之理可乘。故只可用于行地而不可用于耕耘。此则理为气主之明验也。若夫枯槁之物。虽有可用之理。而无生生之气。人死之后。虽有丧祭之理。而无运动之气。此则理无不在。而气或不行之徵也。由此见之。理者包天地万物万事而无所不在者也。气者只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2H 页
 为生物之具。而亦多不备者也。然则气是理中之一物也。理是气之主宰也。岂可以理气之间。以为无分别而合一乎。后世理气之分不明。故皆以为气。而妄行趍蹶是气也而不知制之。打祖骂诸佛是气也而以为性之真。人欲横流。祸至滔天。此莫非知其气而不知理。行其气而灭其理。其害可谓惨矣。而诸儒之说如此。甚可痛也。若夫人心道心之言则尤可笑也。夫性(性是理而已。心是合理气生者也。此云性似差。)者合理气而生之者也。心者虚灵知觉者也。性为一心之主。心为运用之机。是以事物来接之时。心能应之。性乘其机。发其情焉。情之善而不能已者。理之妙而气之精也。情之恶而不能止者。理之反而气之杂也。二者交生于方寸。互有消长之几。此乃人心道心之分歧也。然则气之放肆者。乃为人心。而发而用之。至于乱亡。则岂非至危者耶。理之宰气者。乃为道心。而无声无臭。难可久持。则岂非至微者耶。盖为人欲之恶者。未尝无心而偶为之。必于胸中先有一念为其恶之张本。从此去之则吉。由此行之则凶。故圣人以其念而为危。使之克治焉。为天下之至善者。亦非无志而妄为之。必于心中先有一毫之善念。其念甚微。若存若亡。圣人以为微而使之扩充。此乃天
为生物之具。而亦多不备者也。然则气是理中之一物也。理是气之主宰也。岂可以理气之间。以为无分别而合一乎。后世理气之分不明。故皆以为气。而妄行趍蹶是气也而不知制之。打祖骂诸佛是气也而以为性之真。人欲横流。祸至滔天。此莫非知其气而不知理。行其气而灭其理。其害可谓惨矣。而诸儒之说如此。甚可痛也。若夫人心道心之言则尤可笑也。夫性(性是理而已。心是合理气生者也。此云性似差。)者合理气而生之者也。心者虚灵知觉者也。性为一心之主。心为运用之机。是以事物来接之时。心能应之。性乘其机。发其情焉。情之善而不能已者。理之妙而气之精也。情之恶而不能止者。理之反而气之杂也。二者交生于方寸。互有消长之几。此乃人心道心之分歧也。然则气之放肆者。乃为人心。而发而用之。至于乱亡。则岂非至危者耶。理之宰气者。乃为道心。而无声无臭。难可久持。则岂非至微者耶。盖为人欲之恶者。未尝无心而偶为之。必于胸中先有一念为其恶之张本。从此去之则吉。由此行之则凶。故圣人以其念而为危。使之克治焉。为天下之至善者。亦非无志而妄为之。必于心中先有一毫之善念。其念甚微。若存若亡。圣人以为微而使之扩充。此乃天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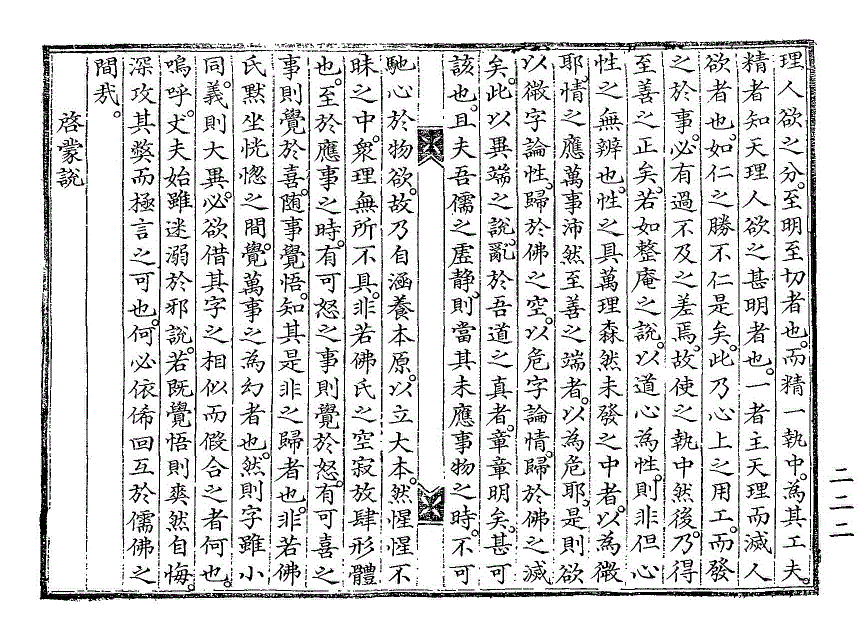 理人欲之分。至明至切者也。而精一执中。为其工夫。精者知天理人欲之甚明者也。一者主天理而灭人欲者也。如仁之胜不仁是矣。此乃心上之用工。而发之于事。必有过不及之差焉。故使之执中然后。乃得至善之正矣。若如整庵之说。以道心为性。则非但心性之无辨也。性之具万理森然未发之中者。以为微耶。情之应万事沛然至善之端者。以为危耶。是则欲以微字论性。归于佛之空。以危字论情。归于佛之灭矣。此以异端之说。乱于吾道之真者。章章明矣。甚可该也。且夫吾儒之虚静。则当其未应事物之时。不可驰心于物欲。故乃自涵养本原。以立大本。然惺惺不昧之中。众理无所不具。非若佛氏之空寂放肆形体也。至于应事之时。有可怒之事则觉于怒。有可喜之事则觉于喜。随事觉悟。知其是非之归者也。非若佛氏默坐恍惚之间。觉万事之为幻者也。然则字虽小同。义则大异。必欲借其字之相似而假合之者何也。呜呼。丈夫始虽迷溺于邪说。若既觉悟则爽然自悔。深攻其弊而极言之可也。何必依俙回互于儒佛之间哉。
理人欲之分。至明至切者也。而精一执中。为其工夫。精者知天理人欲之甚明者也。一者主天理而灭人欲者也。如仁之胜不仁是矣。此乃心上之用工。而发之于事。必有过不及之差焉。故使之执中然后。乃得至善之正矣。若如整庵之说。以道心为性。则非但心性之无辨也。性之具万理森然未发之中者。以为微耶。情之应万事沛然至善之端者。以为危耶。是则欲以微字论性。归于佛之空。以危字论情。归于佛之灭矣。此以异端之说。乱于吾道之真者。章章明矣。甚可该也。且夫吾儒之虚静。则当其未应事物之时。不可驰心于物欲。故乃自涵养本原。以立大本。然惺惺不昧之中。众理无所不具。非若佛氏之空寂放肆形体也。至于应事之时。有可怒之事则觉于怒。有可喜之事则觉于喜。随事觉悟。知其是非之归者也。非若佛氏默坐恍惚之间。觉万事之为幻者也。然则字虽小同。义则大异。必欲借其字之相似而假合之者何也。呜呼。丈夫始虽迷溺于邪说。若既觉悟则爽然自悔。深攻其弊而极言之可也。何必依俙回互于儒佛之间哉。启蒙说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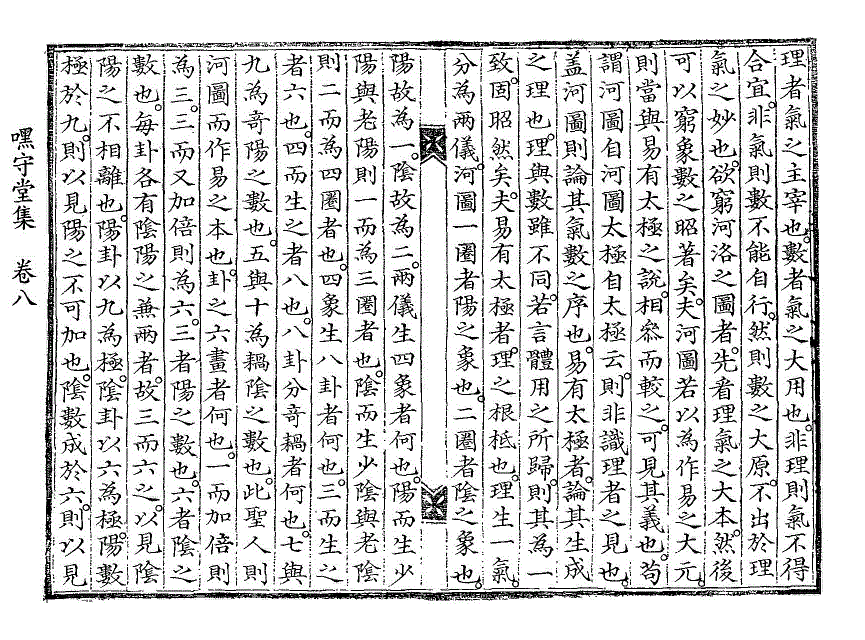 理者气之主宰也。数者气之大用也。非理则气不得合宜。非气则数不能自行。然则数之大原。不出于理气之妙也。欲穷河洛之图者。先看理气之大本。然后可以穷象数之昭著矣。夫河图若以为作易之大元。则当与易有太极之说。相参而较之。可见其义也。苟谓河图自河图太极自太极云。则非识理者之见也。盖河图则论其气数之序也。易有太极者。论其生成之理也。理与数虽不同。若言体用之所归。则其为一致。固昭然矣。夫易有太极者。理之根柢也。理生一气。分为两仪。河图一圈者阳之象也。二圈者阴之象也。阳故为一。阴故为二。两仪生四象者何也。阳而生少阳与老阳则一而为三圈者也。阴而生少阴与老阴则二而为四圈者也。四象生八卦者何也。三而生之者六也。四而生之者八也。八卦分奇耦者何也。七与九为奇阳之数也。五与十为耦阴之数也。此圣人则河图而作易之本也。卦之六画者何也。一而加倍则为三。三而又加倍则为六。三者阳之数也。六者阴之数也。每卦各有阴阳之兼两者。故三而六之。以见阴阳之不相离也。阳卦以九为极。阴卦以六为极。阳数极于九。则以见阳之不可加也。阴数成于六。则以见
理者气之主宰也。数者气之大用也。非理则气不得合宜。非气则数不能自行。然则数之大原。不出于理气之妙也。欲穷河洛之图者。先看理气之大本。然后可以穷象数之昭著矣。夫河图若以为作易之大元。则当与易有太极之说。相参而较之。可见其义也。苟谓河图自河图太极自太极云。则非识理者之见也。盖河图则论其气数之序也。易有太极者。论其生成之理也。理与数虽不同。若言体用之所归。则其为一致。固昭然矣。夫易有太极者。理之根柢也。理生一气。分为两仪。河图一圈者阳之象也。二圈者阴之象也。阳故为一。阴故为二。两仪生四象者何也。阳而生少阳与老阳则一而为三圈者也。阴而生少阴与老阴则二而为四圈者也。四象生八卦者何也。三而生之者六也。四而生之者八也。八卦分奇耦者何也。七与九为奇阳之数也。五与十为耦阴之数也。此圣人则河图而作易之本也。卦之六画者何也。一而加倍则为三。三而又加倍则为六。三者阳之数也。六者阴之数也。每卦各有阴阳之兼两者。故三而六之。以见阴阳之不相离也。阳卦以九为极。阴卦以六为极。阳数极于九。则以见阳之不可加也。阴数成于六。则以见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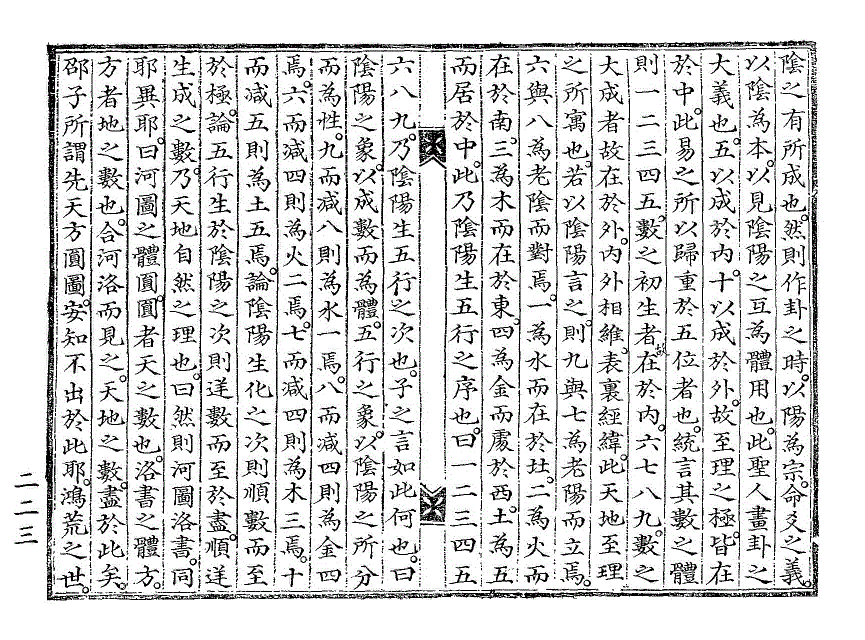 阴之有所成也。然则作卦之时。以阳为宗。命爻之义。以阴为本。以见阴阳之互为体用也。此圣人画卦之大义也。五以成于内。十以成于外。故至理之极。皆在于中。此易之所以归重于五位者也。统言其数之体则一二三四五。数之初生者故在于内。六七八九。数之大成者故在于外。内外相维。表里经纬。此天地至理之所寓也。若以阴阳言之。则九与七为老阳而立焉。六与八为老阴而对焉。一为水而在于北。二为火而在于南。三为木而在于东。四为金而处于西。土为五而居于中。此乃阴阳生五行之序也。曰一二三四五六八九。乃阴阳生五行之次也。子之言如此何也。曰阴阳之象。以成数而为体。五行之象。以阴阳之所分而为性。九而减八则为水一焉。八而减四则为金四焉。六而减四则为火二焉。七而减四则为木三焉。十而减五则为土五焉。论阴阳生化之次则顺数而至于极。论五行生于阴阳之次则逆数而至于尽。顺逆生成之数。乃天地自然之理也。曰然则河图洛书。同耶异耶。曰河图之体圆。圆者天之数也。洛书之体方。方者地之数也。合河洛而见之。天地之数。尽于此矣。邵子所谓先天方圆图。安知不出于此耶。鸿荒之世。
阴之有所成也。然则作卦之时。以阳为宗。命爻之义。以阴为本。以见阴阳之互为体用也。此圣人画卦之大义也。五以成于内。十以成于外。故至理之极。皆在于中。此易之所以归重于五位者也。统言其数之体则一二三四五。数之初生者故在于内。六七八九。数之大成者故在于外。内外相维。表里经纬。此天地至理之所寓也。若以阴阳言之。则九与七为老阳而立焉。六与八为老阴而对焉。一为水而在于北。二为火而在于南。三为木而在于东。四为金而处于西。土为五而居于中。此乃阴阳生五行之序也。曰一二三四五六八九。乃阴阳生五行之次也。子之言如此何也。曰阴阳之象。以成数而为体。五行之象。以阴阳之所分而为性。九而减八则为水一焉。八而减四则为金四焉。六而减四则为火二焉。七而减四则为木三焉。十而减五则为土五焉。论阴阳生化之次则顺数而至于极。论五行生于阴阳之次则逆数而至于尽。顺逆生成之数。乃天地自然之理也。曰然则河图洛书。同耶异耶。曰河图之体圆。圆者天之数也。洛书之体方。方者地之数也。合河洛而见之。天地之数。尽于此矣。邵子所谓先天方圆图。安知不出于此耶。鸿荒之世。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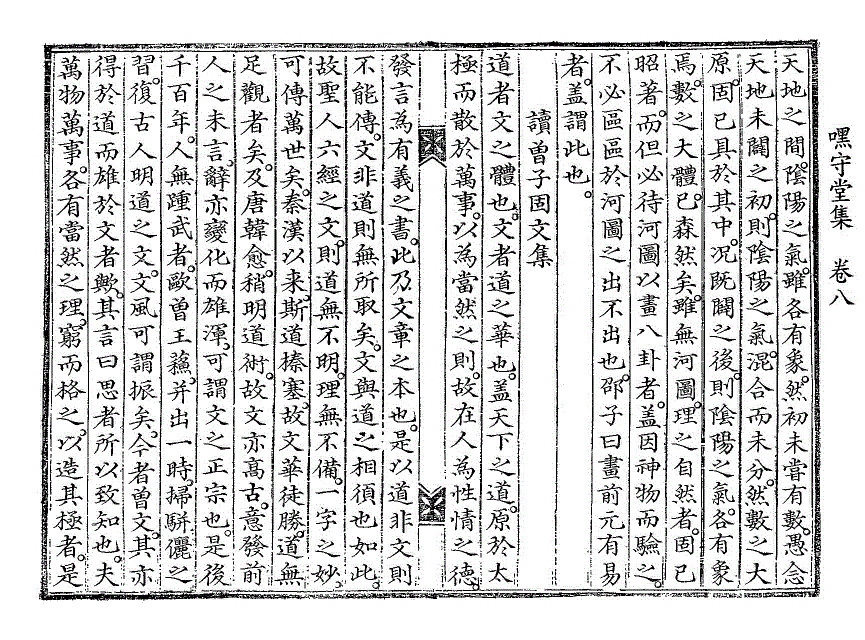 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各有象。然初未尝有数。愚念天地未辟之初。则阴阳之气。混合而未分。然数之大原。固已具于其中。况既辟之后。则阴阳之气。各有象焉。数之大体。已森然矣。虽无河图。理之自然者。固已昭著。而但必待河图以画八卦者。盖因神物而验之。不必区区于河图之出不出也。邵子曰画前元有易者。盖谓此也。
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各有象。然初未尝有数。愚念天地未辟之初。则阴阳之气。混合而未分。然数之大原。固已具于其中。况既辟之后。则阴阳之气。各有象焉。数之大体。已森然矣。虽无河图。理之自然者。固已昭著。而但必待河图以画八卦者。盖因神物而验之。不必区区于河图之出不出也。邵子曰画前元有易者。盖谓此也。读曾子固文集
道者文之体也。文者道之华也。盖天下之道。原于太极而散于万事。以为当然之则。故在人为性情之德。发言为有义之书。此乃文章之本也。是以道非文则不能传。文非道则无所取矣。文与道之相须也如此。故圣人六经之文。则道无不明。理无不备。一字之妙。可传万世矣。秦汉以来。斯道榛塞。故文华徒胜。道无足观者矣。及唐韩愈。稍明道术。故文亦高古。意发前人之未言。辞亦变化而雄浑。可谓文之正宗也。是后千百年。人无踵武者。欧曾王苏。并出一时。扫骈俪之习。复古人明道之文。文风可谓振矣。今者曾文。其亦得于道而雄于文者欤。其言曰思者所以致知也。夫万物万事。各有当然之理。穷而格之。以造其极者。是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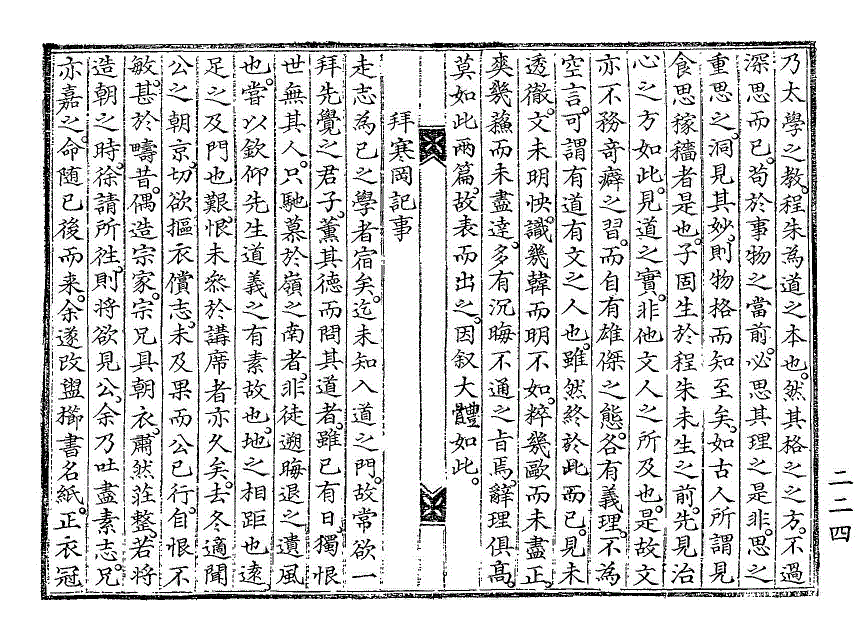 乃太学之教。程朱为道之本也。然其格之之方。不过深思而已。苟于事物之当前。必思其理之是非。思之重思之。洞见其妙。则物格而知至矣。如古人所谓见食思稼穑者是也。子固生于程朱未生之前。先见治心之方如此。见道之实。非他文人之所及也。是故文亦不务奇癖之习。而自有雄杰之态。各有义理。不为空言。可谓有道有文之人也。虽然终于此而已。见未透彻。文未明怏。识几韩而明不如。粹几欧而未尽正。爽几苏而未尽达。多有沉晦不通之旨焉。辞理俱高。莫如此两篇。故表而出之。因叙大体如此。
乃太学之教。程朱为道之本也。然其格之之方。不过深思而已。苟于事物之当前。必思其理之是非。思之重思之。洞见其妙。则物格而知至矣。如古人所谓见食思稼穑者是也。子固生于程朱未生之前。先见治心之方如此。见道之实。非他文人之所及也。是故文亦不务奇癖之习。而自有雄杰之态。各有义理。不为空言。可谓有道有文之人也。虽然终于此而已。见未透彻。文未明怏。识几韩而明不如。粹几欧而未尽正。爽几苏而未尽达。多有沉晦不通之旨焉。辞理俱高。莫如此两篇。故表而出之。因叙大体如此。拜寒冈记事
走志为己之学者宿矣。迄未知入道之门。故常欲一拜先觉之君子。薰其德而问其道者。虽已有日。独恨世无其人。只驰慕于岭之南者。非徒溯晦退之遗风也。尝以钦仰先生道义之有素故也。地之相距也远。足之及门也艰。恨未参于讲席者亦久矣。去冬适闻公之朝京。切欲抠衣偿志。未及果而公已行。自恨不敏。甚于畴昔。偶造宗家。宗兄具朝衣。肃然庄整。若将造朝之时。徐请所往。则将欲见公。余乃吐尽素志。兄亦嘉之。命随己后而来。余遂改盥栉书名纸。正衣冠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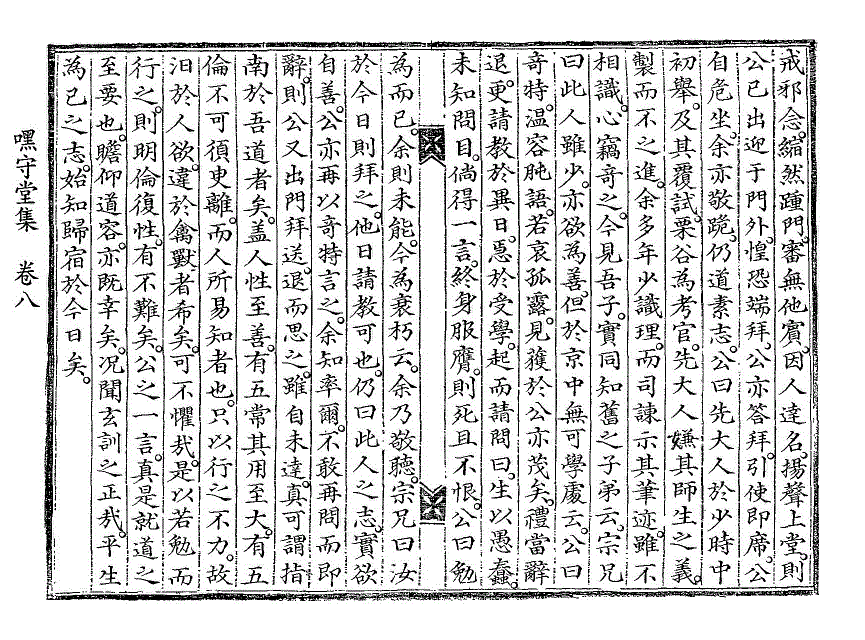 戒邪念。缩然踵门。审无他宾。因人达名。扬声上堂。则公已出迎于门外。惶恐端拜。公亦答拜。引使即席。公自危坐。余亦敬跪。仍道素志。公曰先大人于少时中初举。及其覆试。栗谷为考官。先大人嫌其师生之义。制而不之进。余多年少识理。而司谏示其笔迹。虽不相识。心窃奇之。今见吾子。实同知旧之子弟云。宗兄曰此人虽少。亦欲为善。但于京中无可学处云。公曰奇特。温容肫语。若哀孤露。见获于公亦茂矣。礼当辞退。更请教于异日。急于受学。起而请问曰。生以愚蠢。未知问目。倘得一言。终身服膺。则死且不恨。公曰勉为而已。余则未能。今为衰朽云。余乃敬听。宗兄曰汝于今日则拜之。他日请教可也。仍曰此人之志。实欲自善。公亦再以奇特言之。余知率尔。不敢再问而即辞。则公又出门拜送。退而思之。虽自未达。真可谓指南于吾道者矣。盖人性至善。有五常其用至大。有五伦不可须臾离。而人所易知者也。只以行之不力。故汩于人欲。违于禽兽者希矣。可不惧哉。是以若勉而行之。则明伦复性。有不难矣。公之一言。真是就道之至要也。瞻仰道容。亦既幸矣。况闻玄训之正哉。平生为己之志。始知归宿于今日矣。
戒邪念。缩然踵门。审无他宾。因人达名。扬声上堂。则公已出迎于门外。惶恐端拜。公亦答拜。引使即席。公自危坐。余亦敬跪。仍道素志。公曰先大人于少时中初举。及其覆试。栗谷为考官。先大人嫌其师生之义。制而不之进。余多年少识理。而司谏示其笔迹。虽不相识。心窃奇之。今见吾子。实同知旧之子弟云。宗兄曰此人虽少。亦欲为善。但于京中无可学处云。公曰奇特。温容肫语。若哀孤露。见获于公亦茂矣。礼当辞退。更请教于异日。急于受学。起而请问曰。生以愚蠢。未知问目。倘得一言。终身服膺。则死且不恨。公曰勉为而已。余则未能。今为衰朽云。余乃敬听。宗兄曰汝于今日则拜之。他日请教可也。仍曰此人之志。实欲自善。公亦再以奇特言之。余知率尔。不敢再问而即辞。则公又出门拜送。退而思之。虽自未达。真可谓指南于吾道者矣。盖人性至善。有五常其用至大。有五伦不可须臾离。而人所易知者也。只以行之不力。故汩于人欲。违于禽兽者希矣。可不惧哉。是以若勉而行之。则明伦复性。有不难矣。公之一言。真是就道之至要也。瞻仰道容。亦既幸矣。况闻玄训之正哉。平生为己之志。始知归宿于今日矣。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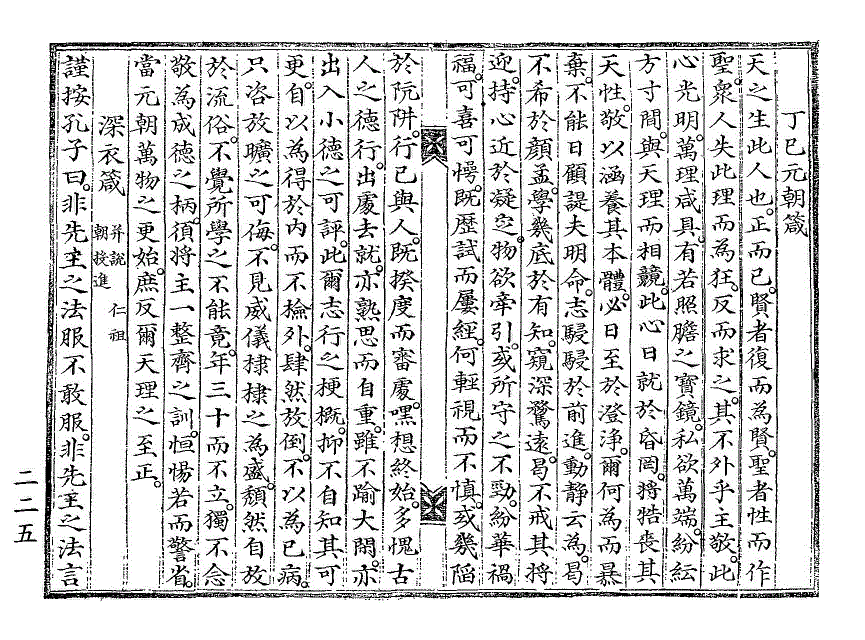 丁巳元朝箴
丁巳元朝箴天之生此人也。正而已。贤者复而为贤。圣者性而作圣。众人失此理而为狂。反而求之。其不外乎主敬。此心光明。万理咸具。有若照胆之宝镜。私欲万端。纷纭方寸间。与天理而相竞。此心日就于昏罔。将牿丧其天性。敬以涵养其本体。必日至于澄净。尔何为而暴弃。不能日顾諟夫明命。志骎骎于前进。动静云为。曷不希于颜孟。学几底于有知。窥深骛远。曷不戒其将迎。持心近于凝定。物欲牵引。或所守之不劲。纷华祸福。可喜可愕。既历试而屡经。何轻视而不慎。或几陷于坑阱。行己与人。既揆度而审处。嘿想终始。多愧古人之德行。出处去就。亦熟思而自重。虽不踰大闲。亦出入小德之可评。此尔志行之梗概。抑不自知其可更。自以为得于内而不检外。肆然放倒。不以为已病。只咨放旷之可侮。不见威仪棣棣之为盛。颓然自放于流俗。不觉所学之不能竟。年三十而不立。独不念敬为成德之柄。须将主一整齐之训。恒惕若而警省。当元朝万物之更始。庶反尔天理之至正。
深衣箴(并说○ 仁祖朝投进)
谨按孔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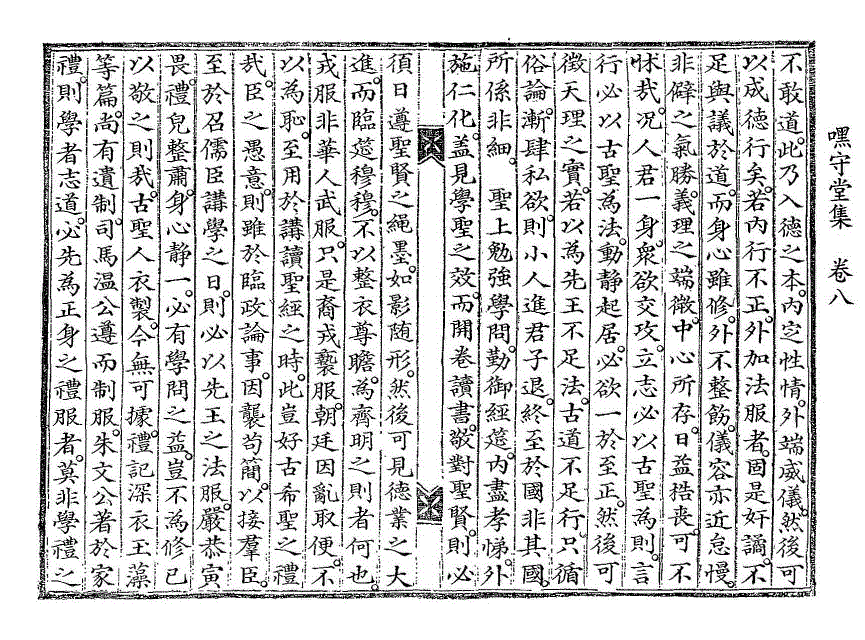 不敢道。此乃入德之本。内定性情。外端威仪。然后可以成德行矣。若内行不正。外加法服者。固是奸谲。不足与议于道。而身心虽修。外不整饬。仪容亦近怠慢。非僻之气胜。义理之端微。中心所存。日益梏丧。可不怵哉。况人君一身。众欲交攻。立志必以古圣为则。言行必以古圣为法。动静起居。必欲一于至正。然后可徵天理之实。若以为先王不足法。古道不足行。只循俗论。渐肆私欲。则小人进君子退。终至于国非其国。所系非细。 圣上勉强学问。勤御经筵。内尽孝悌。外施仁化。盖见学圣之效。而开卷读书。敬对圣贤。则必须日遵圣贤之绳墨。如影随形。然后可见德业之大进。而临筵穆穆。不以整衣尊瞻。为齐明之则者何也。戎服非华人武服。只是裔戎亵服。朝廷因乱取便。不以为耻。至用于讲读圣经之时。此岂好古希圣之礼哉。臣之愚意。则虽于临政论事。因袭苟简。以接群臣。至于召儒臣讲学之日。则必以先王之法服。严恭寅畏。礼皃整肃。身心静一。必有学问之益。岂不为修己以敬之则哉。古圣人衣制。今无可据。礼记深衣玉藻等篇。尚有遗制。司马温公遵而制服。朱文公著于家礼。则学者志道。必先为正身之礼服者。莫非学礼之
不敢道。此乃入德之本。内定性情。外端威仪。然后可以成德行矣。若内行不正。外加法服者。固是奸谲。不足与议于道。而身心虽修。外不整饬。仪容亦近怠慢。非僻之气胜。义理之端微。中心所存。日益梏丧。可不怵哉。况人君一身。众欲交攻。立志必以古圣为则。言行必以古圣为法。动静起居。必欲一于至正。然后可徵天理之实。若以为先王不足法。古道不足行。只循俗论。渐肆私欲。则小人进君子退。终至于国非其国。所系非细。 圣上勉强学问。勤御经筵。内尽孝悌。外施仁化。盖见学圣之效。而开卷读书。敬对圣贤。则必须日遵圣贤之绳墨。如影随形。然后可见德业之大进。而临筵穆穆。不以整衣尊瞻。为齐明之则者何也。戎服非华人武服。只是裔戎亵服。朝廷因乱取便。不以为耻。至用于讲读圣经之时。此岂好古希圣之礼哉。臣之愚意。则虽于临政论事。因袭苟简。以接群臣。至于召儒臣讲学之日。则必以先王之法服。严恭寅畏。礼皃整肃。身心静一。必有学问之益。岂不为修己以敬之则哉。古圣人衣制。今无可据。礼记深衣玉藻等篇。尚有遗制。司马温公遵而制服。朱文公著于家礼。则学者志道。必先为正身之礼服者。莫非学礼之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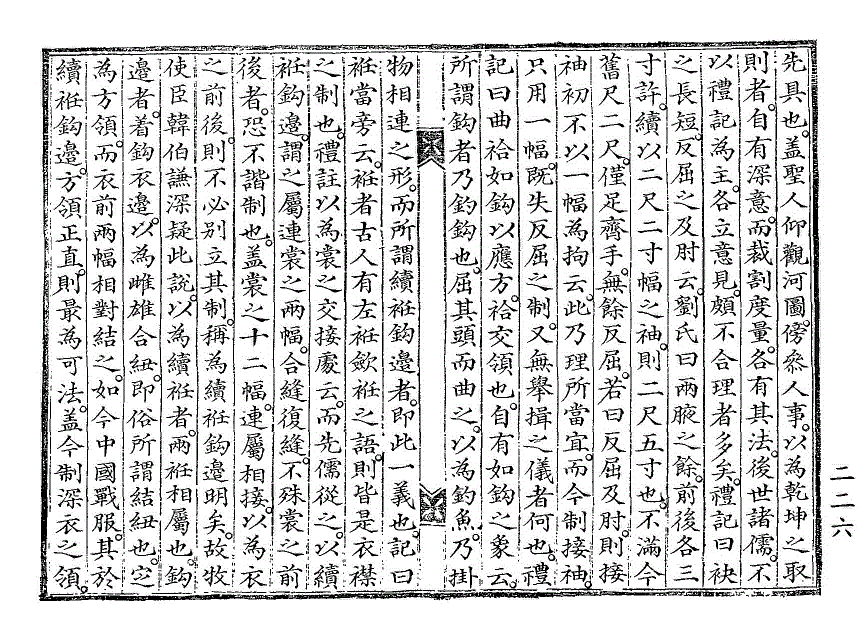 先具也。盖圣人仰观河图。傍参人事。以为乾坤之取则者。自有深意。而裁割度量。各有其法。后世诸儒。不以礼记为主。各立意见。颇不合理者多矣。礼记曰袂之长短。反屈之及肘云。刘氏曰两腋之馀。前后各三寸许。续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则二尺五寸也。不满今旧尺二尺。仅足齐手。无馀反屈。若曰反屈及肘。则接袖初不以一幅为拘云。此乃理所当宜。而今制接袖。只用一幅。既失反屈之制。又无举揖之仪者何也。礼记曰曲袷如钩以应方。袷交领也。自有如钩之象云。所谓钩者乃钓钩也。屈其头而曲之。以为钓鱼。乃挂物相连之形。而所谓续衽钩边者。即此一义也。记曰衽当旁云。衽者古人有左衽敛衽之语。则皆是衣襟之制也。礼注以为裳之交接处云。而先儒从之。以续衽钩边。谓之属连裳之两幅。合缝复缝。不殊裳之前后者。恐不谐制也。盖裳之十二幅。连属相接。以为衣之前后。则不必别立其制。称为续衽钩边明矣。故牧使臣韩伯谦深疑此说。以为续衽者。两衽相属也。钩边者。着钩衣边。以为雌雄合纽。即俗所谓结纽也。定为方领。而衣前两幅相对结之。如今中国战服。其于续衽钩边。方领正直。则最为可法。盖今制深衣之领。
先具也。盖圣人仰观河图。傍参人事。以为乾坤之取则者。自有深意。而裁割度量。各有其法。后世诸儒。不以礼记为主。各立意见。颇不合理者多矣。礼记曰袂之长短。反屈之及肘云。刘氏曰两腋之馀。前后各三寸许。续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则二尺五寸也。不满今旧尺二尺。仅足齐手。无馀反屈。若曰反屈及肘。则接袖初不以一幅为拘云。此乃理所当宜。而今制接袖。只用一幅。既失反屈之制。又无举揖之仪者何也。礼记曰曲袷如钩以应方。袷交领也。自有如钩之象云。所谓钩者乃钓钩也。屈其头而曲之。以为钓鱼。乃挂物相连之形。而所谓续衽钩边者。即此一义也。记曰衽当旁云。衽者古人有左衽敛衽之语。则皆是衣襟之制也。礼注以为裳之交接处云。而先儒从之。以续衽钩边。谓之属连裳之两幅。合缝复缝。不殊裳之前后者。恐不谐制也。盖裳之十二幅。连属相接。以为衣之前后。则不必别立其制。称为续衽钩边明矣。故牧使臣韩伯谦深疑此说。以为续衽者。两衽相属也。钩边者。着钩衣边。以为雌雄合纽。即俗所谓结纽也。定为方领。而衣前两幅相对结之。如今中国战服。其于续衽钩边。方领正直。则最为可法。盖今制深衣之领。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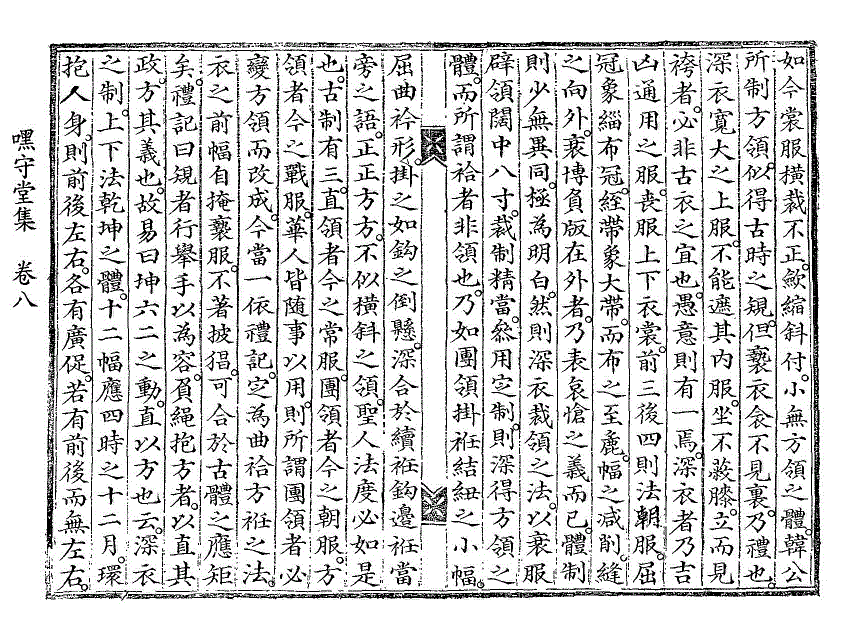 如今裳服横裁不正。敛缩斜付。小无方领之体。韩公所制方领。似得古时之规。但亵衣衾不见里。乃礼也。深衣宽大之上服。不能遮其内服。坐不蔽膝。立而见裤者。必非古衣之宜也。愚意则有一焉。深衣者乃吉凶通用之服。丧服上下衣裳。前三后四则法朝服。屈冠象缁布冠。绖带象大带。而布之至粗。幅之减削。缝之向外。衰博负版在外者。乃表哀怆之义而已。体制则少无异同。极为明白。然则深衣裁领之法。以衰服辟领阔中八寸。裁制精当。参用定制。则深得方领之体。而所谓袷者非领也。乃如团领挂衽结纽之小幅。屈曲衿形。挂之如钩之倒悬。深合于续衽钩边衽当旁之语。正正方方。不似横斜之领。圣人法度必如是也。古制有三。直领者今之常服。团领者今之朝服。方领者今之战服。华人皆随事以用。则所谓团领者必变方领而改成。今当一依礼记。定为曲袷方衽之法。衣之前幅自掩亵服。不著披猖。可合于古体之应矩矣。礼记曰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云。深衣之制。上下法乾坤之体。十二幅应四时之十二月。环抱人身。则前后左右。各有广促。若有前后而无左右。
如今裳服横裁不正。敛缩斜付。小无方领之体。韩公所制方领。似得古时之规。但亵衣衾不见里。乃礼也。深衣宽大之上服。不能遮其内服。坐不蔽膝。立而见裤者。必非古衣之宜也。愚意则有一焉。深衣者乃吉凶通用之服。丧服上下衣裳。前三后四则法朝服。屈冠象缁布冠。绖带象大带。而布之至粗。幅之减削。缝之向外。衰博负版在外者。乃表哀怆之义而已。体制则少无异同。极为明白。然则深衣裁领之法。以衰服辟领阔中八寸。裁制精当。参用定制。则深得方领之体。而所谓袷者非领也。乃如团领挂衽结纽之小幅。屈曲衿形。挂之如钩之倒悬。深合于续衽钩边衽当旁之语。正正方方。不似横斜之领。圣人法度必如是也。古制有三。直领者今之常服。团领者今之朝服。方领者今之战服。华人皆随事以用。则所谓团领者必变方领而改成。今当一依礼记。定为曲袷方衽之法。衣之前幅自掩亵服。不著披猖。可合于古体之应矩矣。礼记曰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云。深衣之制。上下法乾坤之体。十二幅应四时之十二月。环抱人身。则前后左右。各有广促。若有前后而无左右。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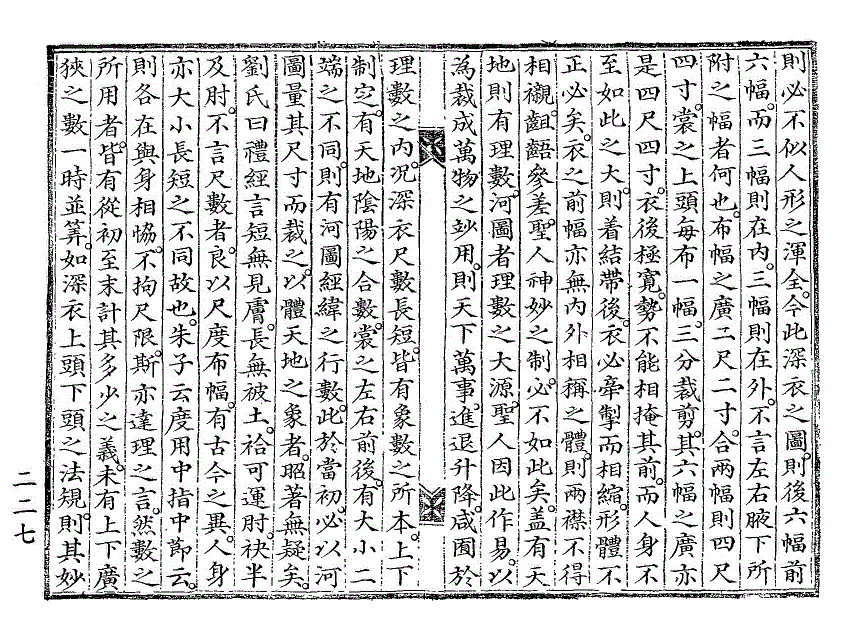 则必不似人形之浑全。今此深衣之图。则后六幅前六幅。而三幅则在内。三幅则在外。不言左右腋下所附之幅者何也。布幅之广二尺二寸。合两幅则四尺四寸。裳之上头每布一幅。三分裁剪。其六幅之广亦是四尺四寸。衣后极宽。势不能相掩其前。而人身不至如此之大。则着结带后。衣必牵掣而相缩。形体不正必矣。衣之前幅亦无内外相称之体。则两襟不得相衬。龃龉参差。圣人神妙之制。必不如此矣。盖有天地则有理数。河图者理数之大源。圣人因此作易。以为裁成万物之妙用。则天下万事。进退升降。咸囿于理数之内。况深衣尺数长短。皆有象数之所本。上下制定。有天地阴阳之合数。裳之左右前后。有大小二端之不同。则有河图经纬之行数。此于当初。必以河图量其尺寸而裁之。以体天地之象者。昭著无疑矣。刘氏曰礼经言短无见肤。长无被土。袷可运肘。袂半及肘。不言尺数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异。人身亦大小长短之不同故也。朱子云度用中指中节云。则各在与身相协。不拘尺限。斯亦达理之言。然数之所用者。皆有从初至末计其多少之义。未有上下广狭之数一时并算。如深衣上头下头之法规。则其妙
则必不似人形之浑全。今此深衣之图。则后六幅前六幅。而三幅则在内。三幅则在外。不言左右腋下所附之幅者何也。布幅之广二尺二寸。合两幅则四尺四寸。裳之上头每布一幅。三分裁剪。其六幅之广亦是四尺四寸。衣后极宽。势不能相掩其前。而人身不至如此之大。则着结带后。衣必牵掣而相缩。形体不正必矣。衣之前幅亦无内外相称之体。则两襟不得相衬。龃龉参差。圣人神妙之制。必不如此矣。盖有天地则有理数。河图者理数之大源。圣人因此作易。以为裁成万物之妙用。则天下万事。进退升降。咸囿于理数之内。况深衣尺数长短。皆有象数之所本。上下制定。有天地阴阳之合数。裳之左右前后。有大小二端之不同。则有河图经纬之行数。此于当初。必以河图量其尺寸而裁之。以体天地之象者。昭著无疑矣。刘氏曰礼经言短无见肤。长无被土。袷可运肘。袂半及肘。不言尺数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异。人身亦大小长短之不同故也。朱子云度用中指中节云。则各在与身相协。不拘尺限。斯亦达理之言。然数之所用者。皆有从初至末计其多少之义。未有上下广狭之数一时并算。如深衣上头下头之法规。则其妙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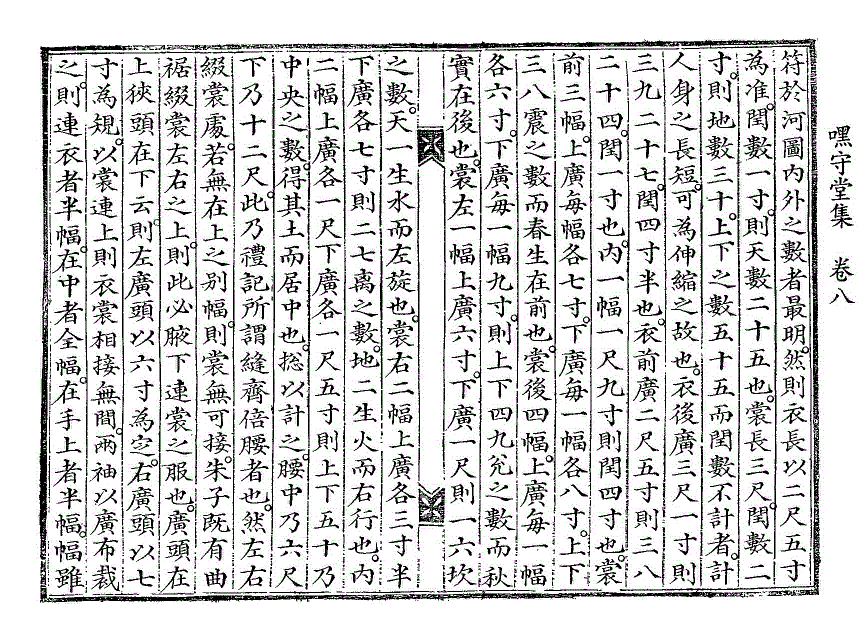 符于河图内外之数者最明。然则衣长以二尺五寸为准。闰数一寸。则天数二十五也。裳长三尺。闰数二寸。则地数三十。上下之数五十五而闰数不计者。计人身之长短。可为伸缩之故也。衣后广三尺一寸则三九二十七。闰四寸半也。衣前广二尺五寸则三八二十四。闰一寸也。内一幅一尺九寸则闰四寸也。裳前三幅。上广每幅各七寸。下广每一幅各八寸。上下三八震之数而春生在前也。裳后四幅。上广每一幅各六寸。下广每一幅九寸。则上下四九兑之数而秋实在后也。裳左一幅上广六寸。下广一尺则一六坎之数。天一生水而左旋也。裳右二幅上广各三寸半下广各七寸则二七离之数。地二生火而右行也。内二幅上广各一尺下广各一尺五寸则上下五十乃中央之数。得其土而居中也。总以计之。腰中乃六尺下乃十二尺。此乃礼记所谓缝齐倍腰者也。然左右缀裳处。若无在上之别幅。则裳无可接。朱子既有曲裾缀裳左右之上。则此必腋下连裳之服也。广头在上狭头在下云。则左广头以六寸为定。右广头以七寸为规。以裳连上则衣裳相接无间。两袖以广布裁之。则连衣者半幅。在中者全幅。在手上者半幅。幅虽
符于河图内外之数者最明。然则衣长以二尺五寸为准。闰数一寸。则天数二十五也。裳长三尺。闰数二寸。则地数三十。上下之数五十五而闰数不计者。计人身之长短。可为伸缩之故也。衣后广三尺一寸则三九二十七。闰四寸半也。衣前广二尺五寸则三八二十四。闰一寸也。内一幅一尺九寸则闰四寸也。裳前三幅。上广每幅各七寸。下广每一幅各八寸。上下三八震之数而春生在前也。裳后四幅。上广每一幅各六寸。下广每一幅九寸。则上下四九兑之数而秋实在后也。裳左一幅上广六寸。下广一尺则一六坎之数。天一生水而左旋也。裳右二幅上广各三寸半下广各七寸则二七离之数。地二生火而右行也。内二幅上广各一尺下广各一尺五寸则上下五十乃中央之数。得其土而居中也。总以计之。腰中乃六尺下乃十二尺。此乃礼记所谓缝齐倍腰者也。然左右缀裳处。若无在上之别幅。则裳无可接。朱子既有曲裾缀裳左右之上。则此必腋下连裳之服也。广头在上狭头在下云。则左广头以六寸为定。右广头以七寸为规。以裳连上则衣裳相接无间。两袖以广布裁之。则连衣者半幅。在中者全幅。在手上者半幅。幅虽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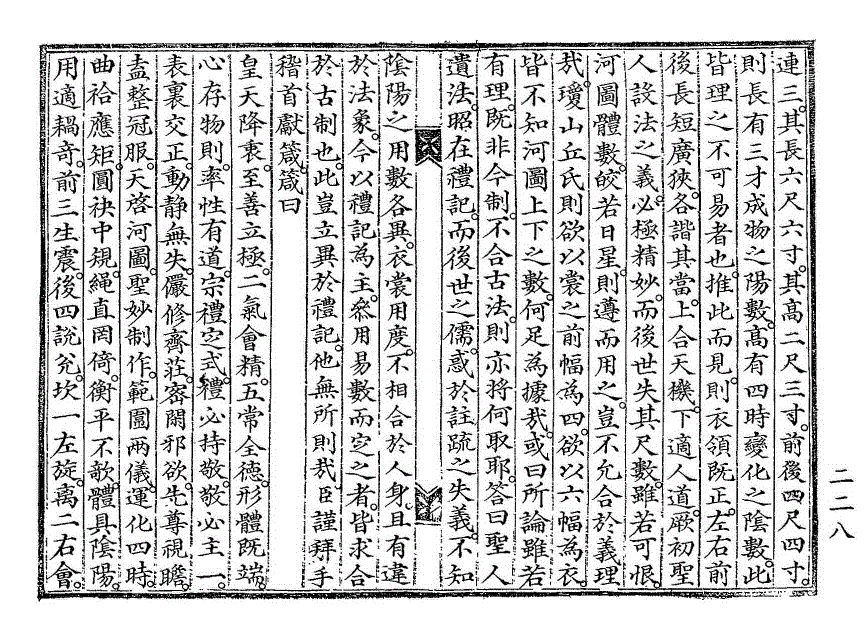 连三。其长六尺六寸。其高二尺三寸。前后四尺四寸。则长有三才成物之阳数。高有四时变化之阴数。此皆理之不可易者也。推此而见。则衣领既正。左右前后长短广狭。各谐其当。上合天机。下适人道。厥初圣人设法之义。必极精妙。而后世失其尺数。虽若可恨。河图体数。皎若日星。则遵而用之。岂不允合于义理哉。琼山丘氏则欲以裳之前幅为四。欲以六幅为衣。皆不知河图上下之数。何足为据哉。或曰所论虽若有理。既非今制。不合古法。则亦将何取耶。答曰圣人遗法。昭在礼记。而后世之儒。惑于注疏之失义。不知阴阳之用数各异。衣裳用度。不相合于人身。且有违于法象。今以礼记为主。参用易数而定之者。皆求合于古制也。此岂立异于礼记。他无所则哉。臣谨拜手稽首献箴。箴曰。
连三。其长六尺六寸。其高二尺三寸。前后四尺四寸。则长有三才成物之阳数。高有四时变化之阴数。此皆理之不可易者也。推此而见。则衣领既正。左右前后长短广狭。各谐其当。上合天机。下适人道。厥初圣人设法之义。必极精妙。而后世失其尺数。虽若可恨。河图体数。皎若日星。则遵而用之。岂不允合于义理哉。琼山丘氏则欲以裳之前幅为四。欲以六幅为衣。皆不知河图上下之数。何足为据哉。或曰所论虽若有理。既非今制。不合古法。则亦将何取耶。答曰圣人遗法。昭在礼记。而后世之儒。惑于注疏之失义。不知阴阳之用数各异。衣裳用度。不相合于人身。且有违于法象。今以礼记为主。参用易数而定之者。皆求合于古制也。此岂立异于礼记。他无所则哉。臣谨拜手稽首献箴。箴曰。皇天降衷。至善立极。二气会精。五常全德。形体既端。心存物则。率性有道。宗礼定式。礼必持敬。敬必主一。表里交正。动静无失。俨修齐庄。密闲邪欲。先尊视瞻。盍整冠服。天启河图。圣妙制作。范围两仪。运化四时。曲袷应矩。圆袂中规。绳直罔倚。衡平不欹。体具阴阳。用适耦奇。前三生震。后四说兑。坎一左旋。离二右会。
嘿守堂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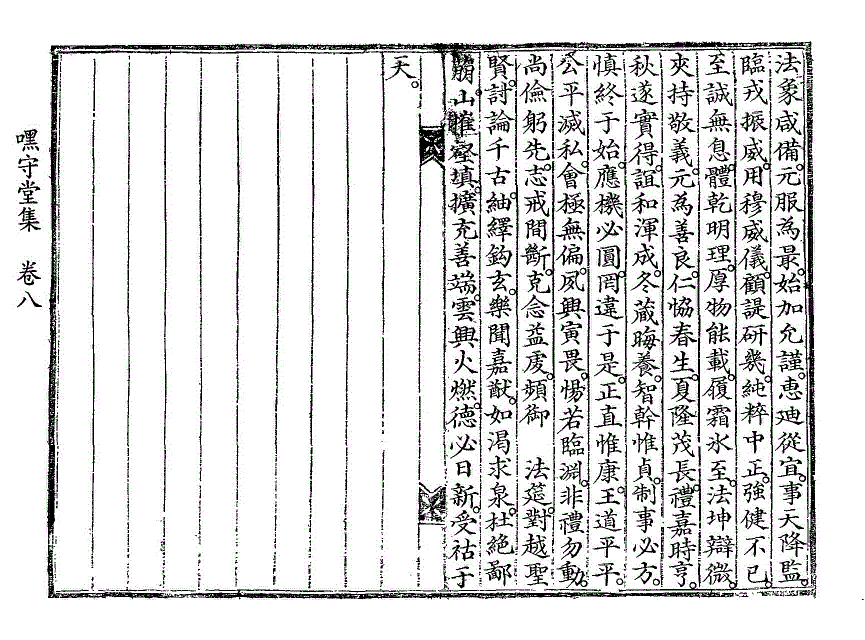 法象咸备。元服为最。始加允谨。惠迪从宜。事天降监。临戎振威。用穆威仪。顾諟研几。纯粹中正。强健不已。至诚无息。体乾明理。厚物能载。履霜冰至。法坤辩微。夹持敬义。元为善良。仁协春生。夏隆茂长。礼嘉时亨。秋遂实得。谊和浑成。冬藏晦养。智干惟贞。制事必方。慎终于始。应机必圆。罔违于是。正直惟康。王道平平。公平灭私。会极无偏。夙兴寅畏。惕若临渊。非礼勿动。尚俭躬先。志戒间断。克念益虔。频御 法筵。对越圣贤。讨论千古。䌷绎钩玄。乐闻嘉猷。如渴求泉。杜绝鄙萌。山摧壑填。扩充善端。云兴火燃。德必日新。受祐于天。
法象咸备。元服为最。始加允谨。惠迪从宜。事天降监。临戎振威。用穆威仪。顾諟研几。纯粹中正。强健不已。至诚无息。体乾明理。厚物能载。履霜冰至。法坤辩微。夹持敬义。元为善良。仁协春生。夏隆茂长。礼嘉时亨。秋遂实得。谊和浑成。冬藏晦养。智干惟贞。制事必方。慎终于始。应机必圆。罔违于是。正直惟康。王道平平。公平灭私。会极无偏。夙兴寅畏。惕若临渊。非礼勿动。尚俭躬先。志戒间断。克念益虔。频御 法筵。对越圣贤。讨论千古。䌷绎钩玄。乐闻嘉猷。如渴求泉。杜绝鄙萌。山摧壑填。扩充善端。云兴火燃。德必日新。受祐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