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银槎日录]
[银槎日录]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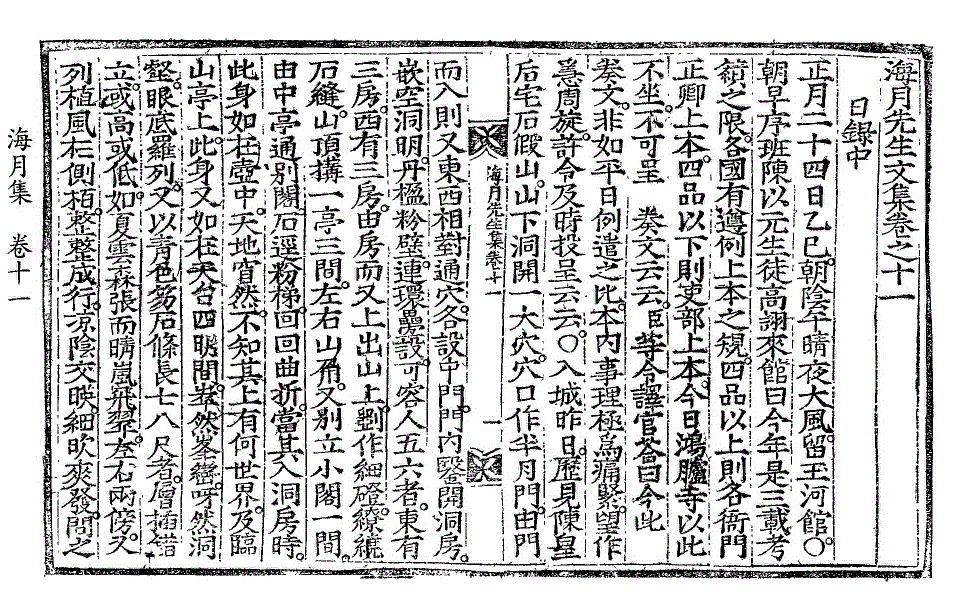 日录中
日录中[己亥正月]
正月二十四日乙巳。朝阴午晴夜大风。留玉河馆。○朝早序班陈以元生徒高诩来馆曰今年是三载考绩之限。各国有遵例上本之规。四品以上则各衙门正卿上本。四品以下则吏部上本。今日鸿胪寺以此不坐。不可呈 奏文云云。臣等令译官答曰今此 奏文。非如平日例遣之比。本内事理极为痛紧。望作急周旋。许令及时投呈云云。○入城昨日。历见陈皇后宅石假山。山下洞开一大穴。穴口作半月门。由门而入则又东西相对通穴。各设中门。门内凿开洞房。嵌空洞明。丹楹粉壁。连环叠设。可容人五六者。东有三房。西有三房。由房而又上出山上。㓸作细磴。缭绕石缝。山顶搆一亭三间。左右山角。又别立小阁一间。由中亭通别阁。石径粉梯。回回曲折。当其入洞房时。此身如在壶中。天地窅然。不知其上有何世界。及临山亭上。此身又如在天台四明间。崒然峰峦。呀然洞壑。眼底罗列。又以青色笏石条长七八尺者。层插错立。或高或低。如夏云森张而晴岚飞翠。左右两傍。又列植风杉侧柏。整整成行。凉阴交映。细欥爽发。问之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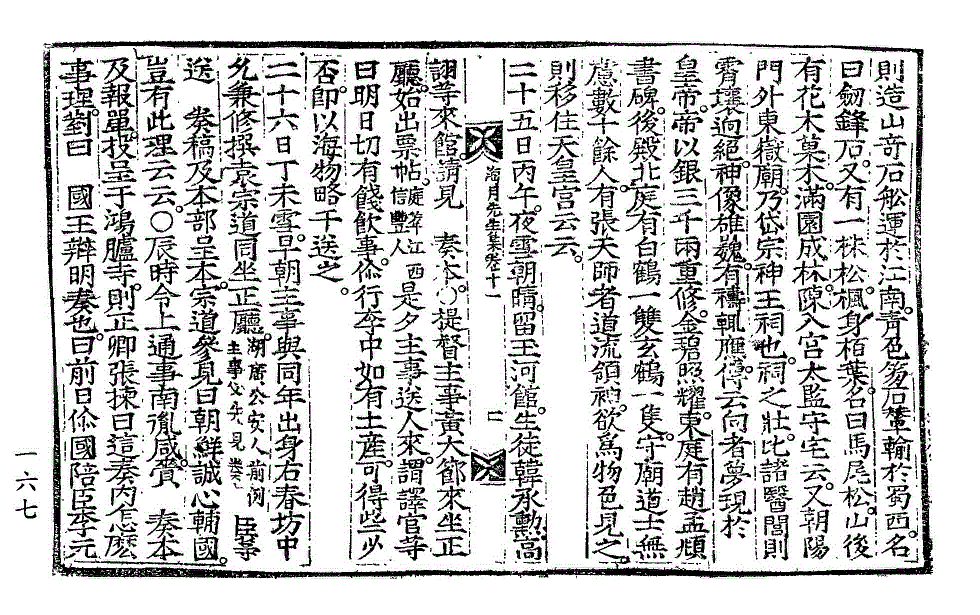 则造山奇石船运于江南。青色笏石辇输于蜀西。名曰剑锋石。又有一株松。枫身柏叶。名曰马尾松。山后有花木果木。满园成林。陈入宫太监守宅云。又朝阳门外东岳庙。乃岱宗神王祠也。祠之壮。比诸医闾则霄壤迥绝。神像雄巍。有祷辄应。传云向者梦现于 皇帝。帝以银三千两重修。金碧照耀。东庭有赵孟頫书碑。后殿北庭有白鹤一双。玄鹤一只守庙道士无虑数十馀人。有张天师者道流领袖。欲为物色见之。则移住天皇宫云云。
则造山奇石船运于江南。青色笏石辇输于蜀西。名曰剑锋石。又有一株松。枫身柏叶。名曰马尾松。山后有花木果木。满园成林。陈入宫太监守宅云。又朝阳门外东岳庙。乃岱宗神王祠也。祠之壮。比诸医闾则霄壤迥绝。神像雄巍。有祷辄应。传云向者梦现于 皇帝。帝以银三千两重修。金碧照耀。东庭有赵孟頫书碑。后殿北庭有白鹤一双。玄鹤一只守庙道士无虑数十馀人。有张天师者道流领袖。欲为物色见之。则移住天皇宫云云。二十五日丙午。夜雪朝晴。留玉河馆。生徒韩承勋,高诩等来馆。请见 奏本。○提督主事黄大节来坐正厅。始出票帖。(庭萃江西信丰人)是夕主事送人来。谓译官等曰明日切有饯饮事。你行李中如有土产。可得些少否。即以海物略干送之。
二十六日丁未雪。早朝主事与同年出身右春坊中允兼修撰袁宗道同坐正厅。(湖广公安人前例主事必先见奏本)臣等送 奏稿及本部呈本。宗道参见曰朝鲜诚心辅国。岂有此理云云。○辰时令上通事南胤咸。赍 奏本及报单。投呈于鸿胪寺。则正卿张拣曰这奏内怎么事理。对曰 国王辨明奏也。曰前日你国陪臣李元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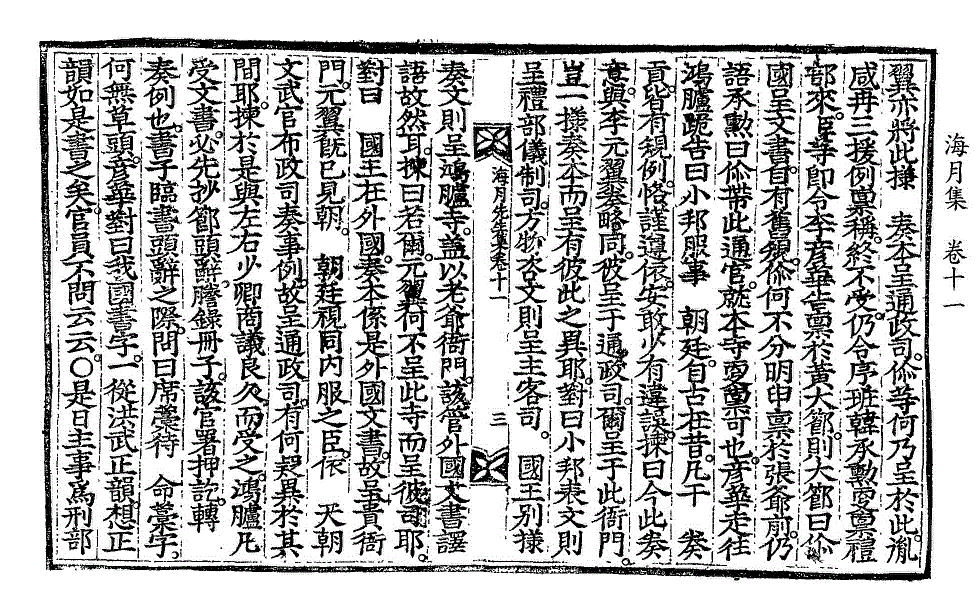 翼亦将此样 奏本呈通政司。你等何乃呈于此。胤咸再三援例禀称。终不受。仍令序班韩承勋更禀礼部来。臣等即令李彦华告禀于黄大节。则大节曰你国呈文书。自有旧规。你何不分明申禀于张爷前。仍语承勋曰你带此通官。就本寺更禀可也。彦华走往鸿胪跪告曰小邦服事 朝廷。自古在昔。凡干 奏贡。皆有规例。恪谨遵依。安敢少有违误。拣曰今此奏意。与李元翼奏略同。彼呈于通政司。尔呈于此衙门。岂一样奏本而呈有彼此之异耶。对曰小邦表文则呈礼部仪制司。方物咨文则呈主客司。 国王别样奏文则呈鸿胪寺。盖以老爷衙门。该管外国文书译语故然耳。拣曰若尔。元翼何不呈此寺而呈彼司耶。对曰 国王在外国。奏本系是外国文书。故呈贵衙门。元翼既已见朝。 朝廷视同内服之臣。依 天朝文武官布政司奏事例。故呈通政司。有何疑异于其间耶。拣于是与左右少卿商议良久而受之。鸿胪凡受文书。必先抄节头辞。誊录册子。该官署押讫。转 奏例也。书子临书头辞之际。问曰席藁待 命藁字。何无草头。彦华对曰我国书字。一从洪武正韵。想正韵如是书之矣。官员不问云云。○是日主事为刑部
翼亦将此样 奏本呈通政司。你等何乃呈于此。胤咸再三援例禀称。终不受。仍令序班韩承勋更禀礼部来。臣等即令李彦华告禀于黄大节。则大节曰你国呈文书。自有旧规。你何不分明申禀于张爷前。仍语承勋曰你带此通官。就本寺更禀可也。彦华走往鸿胪跪告曰小邦服事 朝廷。自古在昔。凡干 奏贡。皆有规例。恪谨遵依。安敢少有违误。拣曰今此奏意。与李元翼奏略同。彼呈于通政司。尔呈于此衙门。岂一样奏本而呈有彼此之异耶。对曰小邦表文则呈礼部仪制司。方物咨文则呈主客司。 国王别样奏文则呈鸿胪寺。盖以老爷衙门。该管外国文书译语故然耳。拣曰若尔。元翼何不呈此寺而呈彼司耶。对曰 国王在外国。奏本系是外国文书。故呈贵衙门。元翼既已见朝。 朝廷视同内服之臣。依 天朝文武官布政司奏事例。故呈通政司。有何疑异于其间耶。拣于是与左右少卿商议良久而受之。鸿胪凡受文书。必先抄节头辞。誊录册子。该官署押讫。转 奏例也。书子临书头辞之际。问曰席藁待 命藁字。何无草头。彦华对曰我国书字。一从洪武正韵。想正韵如是书之矣。官员不问云云。○是日主事为刑部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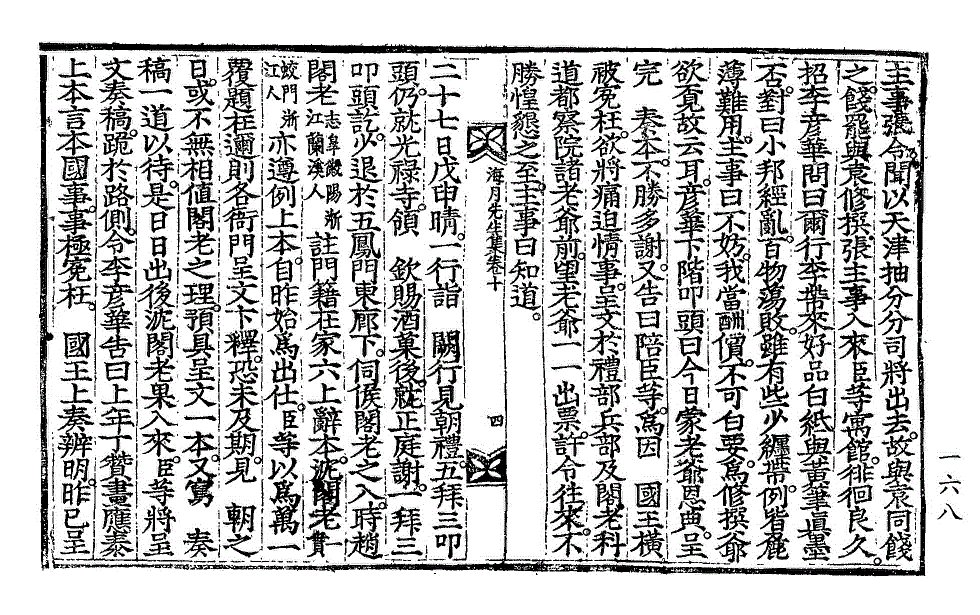 主事张令。闻以天津抽分分司将出去。故与袁同饯之。饯罢与袁修撰,张主事入来臣等寓馆。徘徊良久。招李彦华问曰尔行李带来好品白纸与黄笔真墨否。对曰小邦经乱。百物荡败。虽有些少缠带。例皆粗薄难用。主事曰不妨。我当酬价。不可白要。为修撰爷欲觅故云耳。彦华下阶叩头曰今日蒙老爷恩典。呈完 奏本。不胜多谢。又告曰陪臣等。为因 国王横被冤枉。欲将痛迫情事。呈文于礼部兵部及阁老科道都察院诸老爷前。望老爷一一出票。许令往来。不胜惶恳之至。主事曰知道。
主事张令。闻以天津抽分分司将出去。故与袁同饯之。饯罢与袁修撰,张主事入来臣等寓馆。徘徊良久。招李彦华问曰尔行李带来好品白纸与黄笔真墨否。对曰小邦经乱。百物荡败。虽有些少缠带。例皆粗薄难用。主事曰不妨。我当酬价。不可白要。为修撰爷欲觅故云耳。彦华下阶叩头曰今日蒙老爷恩典。呈完 奏本。不胜多谢。又告曰陪臣等。为因 国王横被冤枉。欲将痛迫情事。呈文于礼部兵部及阁老科道都察院诸老爷前。望老爷一一出票。许令往来。不胜惶恳之至。主事曰知道。二十七日戊申晴。一行诣 阙行见朝礼。五拜三叩头。仍就光禄寺。领 钦赐酒果后。就正庭谢。一拜三叩头讫。少退于五凤门东廊下。伺候阁老之入。时赵阁老(志皋徽阳浙江兰溪人)注门籍在家六上辞本。沈阁老(一贯蛟门浙江人)亦遵例上本。自昨始为出仕。臣等以为万一覆题在迩则各衙门呈文卞释。恐未及期。见 朝之日。或不无相值阁老之理。预具呈文一本。又写 奏稿一道以待。是日日出后沈阁老果入来。臣等将呈文奏稿。跪于路侧。令李彦华告曰上年丁赞画应泰上本言本国事。事极冤枉。 国王上奏辨明。昨已呈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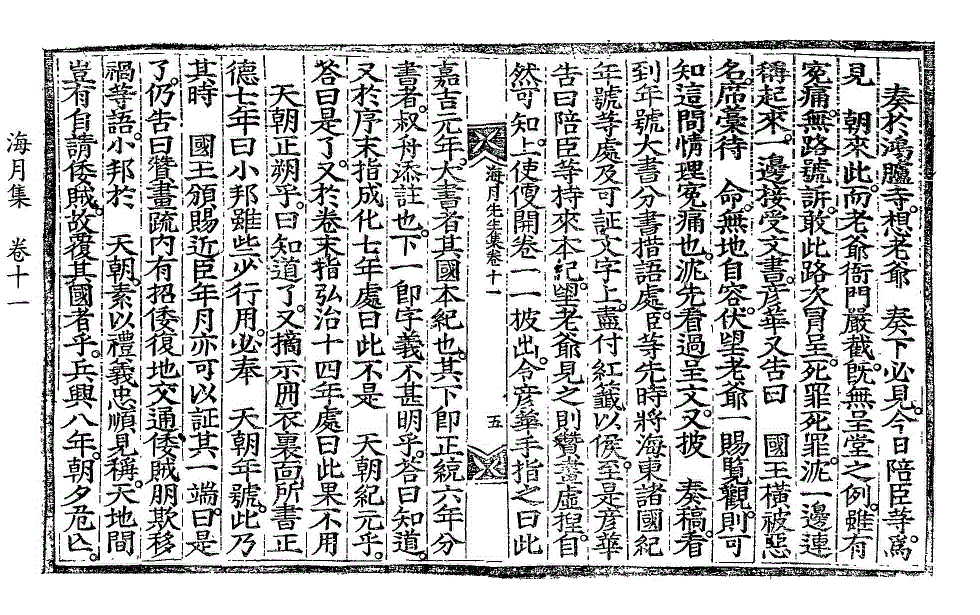 奏于鸿胪寺。想老爷 奏下必见。今日陪臣等。为见 朝来此。而老爷衙门严截。既无呈堂之例。虽有冤痛。无路号诉。敢此路次冒呈。死罪死罪。沈一边连称起来。一边接受文书。彦华又告曰 国王横被恶名。席藁待 命。无地自容。伏望老爷一赐览观。则可知这间情理冤痛也。沈先看过呈文。又披 奏稿。看到年号大书分书措语处。臣等先时将海东诸国纪年号等处及可證文字上。尽付红签以候。至是彦华告曰陪臣等持来本纪。望老爷见之则赞画虚捏。自然可知。上使便开卷一一披出。令彦华手指之曰此嘉吉元年。大书者其国本纪也。其下即正统六年分书者。叔舟添注也。下一即字义不甚明乎。答曰知道。又于序末指成化七年处曰此不是 天朝纪元乎。答曰是了。又于卷末指弘治十四年处曰此果不用 天朝正朔乎。曰知道了。又摘示册衣里面所书正德七年曰小邦虽些少行用。必奉 天朝年号。此乃其时 国王颁赐近臣年月亦可以证其一端曰是了。仍告曰赞画疏内有招倭复地交通倭贼朋欺移祸等语。小邦于 天朝。素以礼义忠顺见称。天地间岂有自请倭贼。故覆其国者乎。兵兴八年。朝夕危亡。
奏于鸿胪寺。想老爷 奏下必见。今日陪臣等。为见 朝来此。而老爷衙门严截。既无呈堂之例。虽有冤痛。无路号诉。敢此路次冒呈。死罪死罪。沈一边连称起来。一边接受文书。彦华又告曰 国王横被恶名。席藁待 命。无地自容。伏望老爷一赐览观。则可知这间情理冤痛也。沈先看过呈文。又披 奏稿。看到年号大书分书措语处。臣等先时将海东诸国纪年号等处及可證文字上。尽付红签以候。至是彦华告曰陪臣等持来本纪。望老爷见之则赞画虚捏。自然可知。上使便开卷一一披出。令彦华手指之曰此嘉吉元年。大书者其国本纪也。其下即正统六年分书者。叔舟添注也。下一即字义不甚明乎。答曰知道。又于序末指成化七年处曰此不是 天朝纪元乎。答曰是了。又于卷末指弘治十四年处曰此果不用 天朝正朔乎。曰知道了。又摘示册衣里面所书正德七年曰小邦虽些少行用。必奉 天朝年号。此乃其时 国王颁赐近臣年月亦可以证其一端曰是了。仍告曰赞画疏内有招倭复地交通倭贼朋欺移祸等语。小邦于 天朝。素以礼义忠顺见称。天地间岂有自请倭贼。故覆其国者乎。兵兴八年。朝夕危亡。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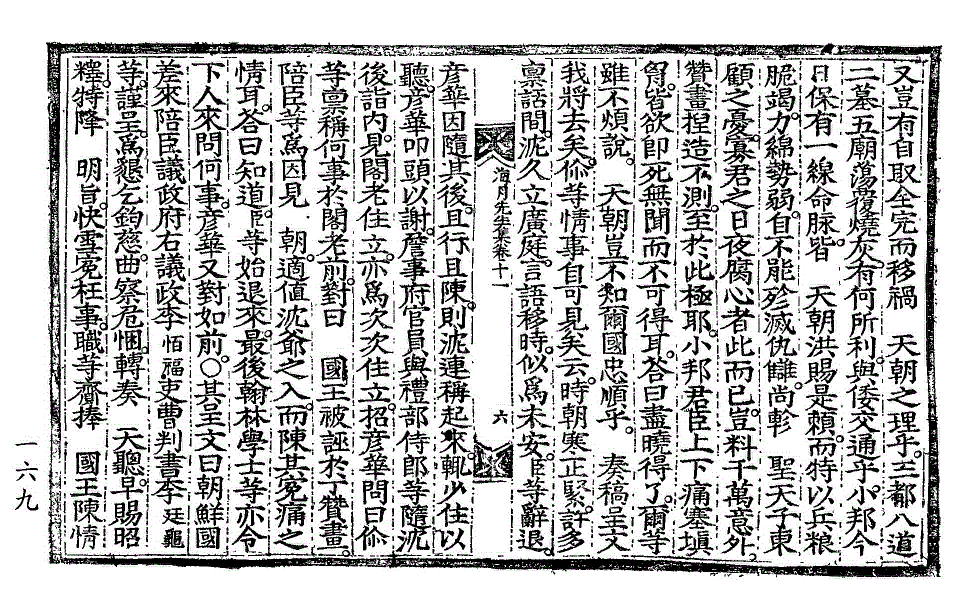 又岂有自取全完而移祸 天朝之理乎。三都八道二墓五庙荡覆烧灰。有何所利。与倭交通乎。小邦今日保有一线命脉。皆 天朝洪赐是赖。而特以兵粮脆竭。力绵势弱。自不能殄灭仇雠。尚轸 圣天子东顾之忧。寡君之日夜腐心者此而已。岂料千万意外。赞画捏造不测。至于此极耶。小邦君臣上下痛塞填胸。皆欲即死无闻而不可得耳。答曰尽晓得了。尔等虽不烦说。 天朝岂不知尔国忠顺乎。 奏稿呈文我将去矣。你等情事自可见矣。云。时朝寒正紧。许多禀话间。沈久立广庭。言语移时。似为未安臣等辞退。彦华因随其后。且行且陈。则沈连称起来。辄少住以听。彦华叩头以谢。詹事府官员与礼部侍郎等随沈后诣内。见阁老住立。亦为次次住立。招彦华问曰你等禀称何事于阁老前。对曰 国王被诬于丁赞画。陪臣等为因见 朝。适值沈爷之入。而陈其冤痛之情耳。答曰知道。臣等始退来。最后翰林学士等亦令下人来问何事。彦华又对如前。○其呈文曰朝鲜国差来陪臣议政府右议政李(恒福),吏曹判书李(廷龟)等。谨呈。为恳乞钩慈。曲察危悃。转奏 天聪。早赐昭释。特降 明旨。快雪冤枉事。职等赍捧 国王陈情
又岂有自取全完而移祸 天朝之理乎。三都八道二墓五庙荡覆烧灰。有何所利。与倭交通乎。小邦今日保有一线命脉。皆 天朝洪赐是赖。而特以兵粮脆竭。力绵势弱。自不能殄灭仇雠。尚轸 圣天子东顾之忧。寡君之日夜腐心者此而已。岂料千万意外。赞画捏造不测。至于此极耶。小邦君臣上下痛塞填胸。皆欲即死无闻而不可得耳。答曰尽晓得了。尔等虽不烦说。 天朝岂不知尔国忠顺乎。 奏稿呈文我将去矣。你等情事自可见矣。云。时朝寒正紧。许多禀话间。沈久立广庭。言语移时。似为未安臣等辞退。彦华因随其后。且行且陈。则沈连称起来。辄少住以听。彦华叩头以谢。詹事府官员与礼部侍郎等随沈后诣内。见阁老住立。亦为次次住立。招彦华问曰你等禀称何事于阁老前。对曰 国王被诬于丁赞画。陪臣等为因见 朝。适值沈爷之入。而陈其冤痛之情耳。答曰知道。臣等始退来。最后翰林学士等亦令下人来问何事。彦华又对如前。○其呈文曰朝鲜国差来陪臣议政府右议政李(恒福),吏曹判书李(廷龟)等。谨呈。为恳乞钩慈。曲察危悃。转奏 天聪。早赐昭释。特降 明旨。快雪冤枉事。职等赍捧 国王陈情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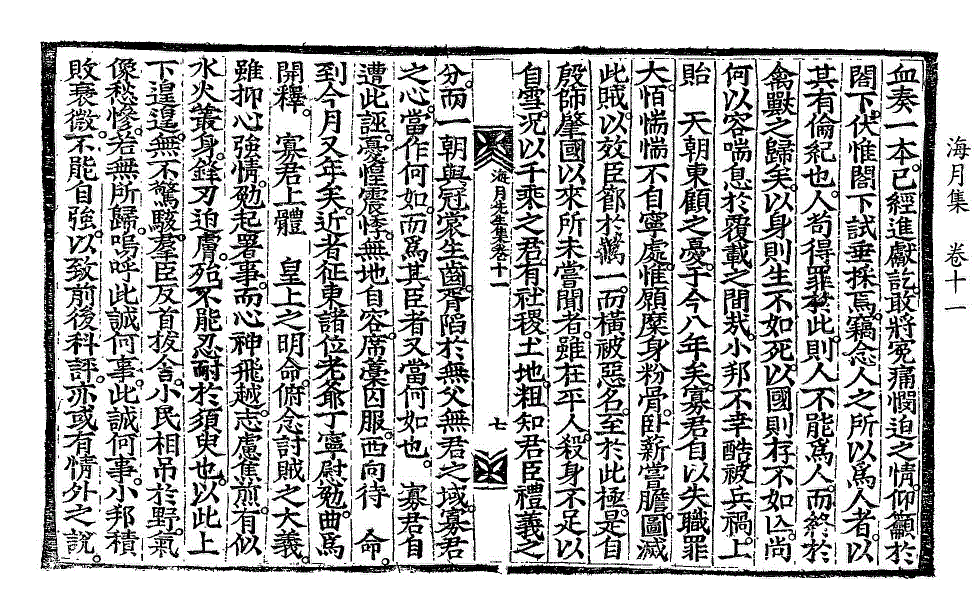 血奏一本。已经进献讫。敢将冤痛悯迫之情。仰吁于閤下。伏惟閤下试垂采焉。窃念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伦纪也。人苟得罪于此。则人不能为人。而终于禽兽之归矣。以身则生不如死。以国则存不如亡。尚何以容喘息于覆载之间哉。小邦不幸酷被兵祸。上贻 天朝东顾之忧。于今八年矣。寡君自以失职罪大。恒惴惴不自宁处。惟愿糜身粉骨。卧薪尝胆。图灭此贼。以效臣节于万一。而横被恶名。至于此极。是自殷师肇国以来所未尝闻者。虽在平人。杀身不足以自雪。况以千乘之君。有社稷土地。粗知君臣礼义之分。而一朝与冠裳生齿。胥陷于无父无君之域。寡君之心。当作何如。而为其臣者又当何如也。 寡君自遭此诬。忧惶震悸。无地自容。席藁囚服。西向待 命到今月又年矣。近者征东诸位老爷丁宁慰勉。曲为开释 寡君上体 皇上之明命。俯念讨贼之大义。虽抑心强情。勉起署事。而心神飞越。志虑焦煎。有似水火丛身。锋刃迫肤。殆不能忍耐于须臾也。以此上下遑遑。无不惊骇。群臣反首拔舍。小民相吊于野。气像愁惨。若无所归。呜呼。此诚何事。此诚何事。小邦积败衰微。不能自强。以致前后科评。亦或有情外之说。
血奏一本。已经进献讫。敢将冤痛悯迫之情。仰吁于閤下。伏惟閤下试垂采焉。窃念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伦纪也。人苟得罪于此。则人不能为人。而终于禽兽之归矣。以身则生不如死。以国则存不如亡。尚何以容喘息于覆载之间哉。小邦不幸酷被兵祸。上贻 天朝东顾之忧。于今八年矣。寡君自以失职罪大。恒惴惴不自宁处。惟愿糜身粉骨。卧薪尝胆。图灭此贼。以效臣节于万一。而横被恶名。至于此极。是自殷师肇国以来所未尝闻者。虽在平人。杀身不足以自雪。况以千乘之君。有社稷土地。粗知君臣礼义之分。而一朝与冠裳生齿。胥陷于无父无君之域。寡君之心。当作何如。而为其臣者又当何如也。 寡君自遭此诬。忧惶震悸。无地自容。席藁囚服。西向待 命到今月又年矣。近者征东诸位老爷丁宁慰勉。曲为开释 寡君上体 皇上之明命。俯念讨贼之大义。虽抑心强情。勉起署事。而心神飞越。志虑焦煎。有似水火丛身。锋刃迫肤。殆不能忍耐于须臾也。以此上下遑遑。无不惊骇。群臣反首拔舍。小民相吊于野。气像愁惨。若无所归。呜呼。此诚何事。此诚何事。小邦积败衰微。不能自强。以致前后科评。亦或有情外之说。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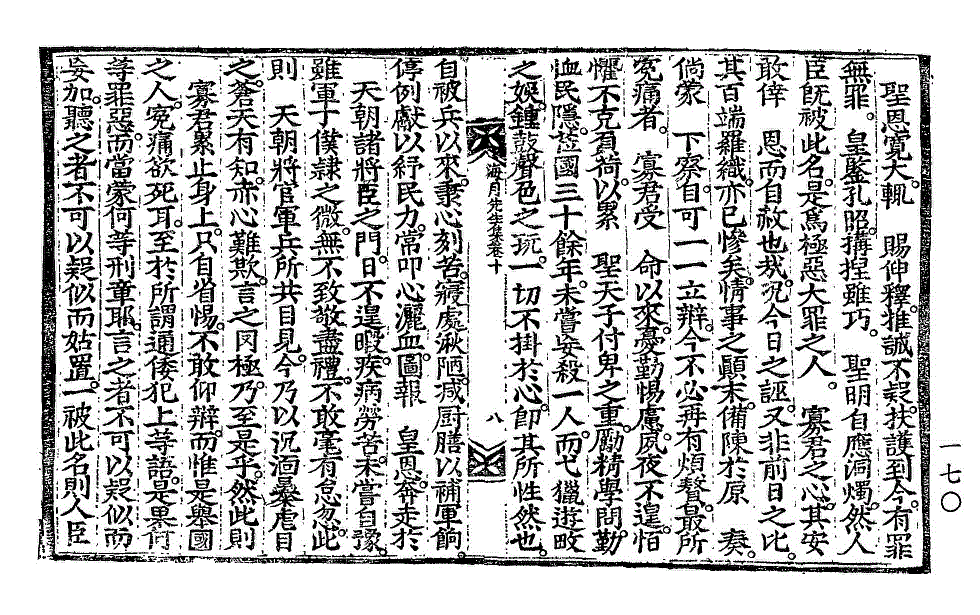 圣恩宽大。辄 赐伸释。推诚不疑。扶护到今。有罪无罪 皇鉴孔昭。搆捏虽巧。 圣明自应洞烛。然人臣既被此名。是为极恶大罪之人。 寡君之心。其安敢倖 恩而自赦也哉。况今日之诬。又非前日之比。其百端罗织。亦已惨矣。情事之颠末。备陈于原 奏。倘蒙 下察。自可一一立辨。今不必再有烦赘。最所冤痛者。 寡君受 命以来。忧勤惕虑。夙夜不遑。恒惧不克负荷。以累 圣天子付畀之重。励精学问。勤恤民隐。莅国三十馀年。未尝妄杀一人。而弋猎游畋之娱。钟鼓声色之玩。一切不挂于心。即其所性然也。自被兵以来。秉心刻苦寝处湫陋。减厨膳以补军饷。停例献以纾民力。常叩心洒血。图报 皇恩。奔走于 天朝诸将臣之门。日不遑暇。疾病劳苦。未尝自豫。虽军丁仆隶之微。无不致敬尽礼。不敢毫有怠忽。此则 天朝将官军兵所共目见。今乃以沉湎暴虐目之。苍天有知。赤心难欺。言之罔极。乃至是乎。然此则 寡君累止身上。只自省惕。不敢仰辨。而惟是举国之人。冤痛欲死耳。至于所谓通倭犯上等语。是果何等罪恶。而当蒙何等刑章耶。言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妄加。听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姑置。一被此名则人臣
圣恩宽大。辄 赐伸释。推诚不疑。扶护到今。有罪无罪 皇鉴孔昭。搆捏虽巧。 圣明自应洞烛。然人臣既被此名。是为极恶大罪之人。 寡君之心。其安敢倖 恩而自赦也哉。况今日之诬。又非前日之比。其百端罗织。亦已惨矣。情事之颠末。备陈于原 奏。倘蒙 下察。自可一一立辨。今不必再有烦赘。最所冤痛者。 寡君受 命以来。忧勤惕虑。夙夜不遑。恒惧不克负荷。以累 圣天子付畀之重。励精学问。勤恤民隐。莅国三十馀年。未尝妄杀一人。而弋猎游畋之娱。钟鼓声色之玩。一切不挂于心。即其所性然也。自被兵以来。秉心刻苦寝处湫陋。减厨膳以补军饷。停例献以纾民力。常叩心洒血。图报 皇恩。奔走于 天朝诸将臣之门。日不遑暇。疾病劳苦。未尝自豫。虽军丁仆隶之微。无不致敬尽礼。不敢毫有怠忽。此则 天朝将官军兵所共目见。今乃以沉湎暴虐目之。苍天有知。赤心难欺。言之罔极。乃至是乎。然此则 寡君累止身上。只自省惕。不敢仰辨。而惟是举国之人。冤痛欲死耳。至于所谓通倭犯上等语。是果何等罪恶。而当蒙何等刑章耶。言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妄加。听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姑置。一被此名则人臣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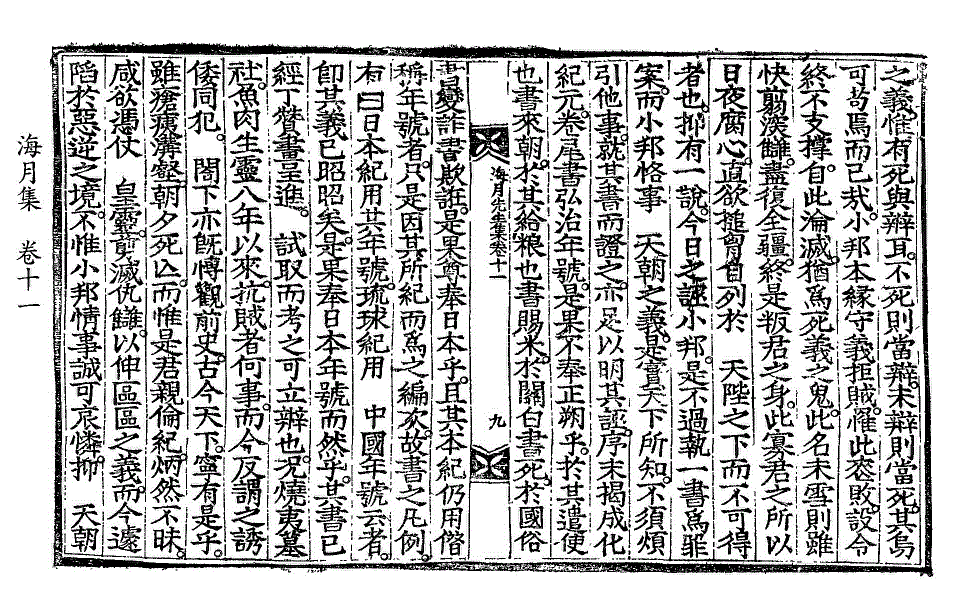 之义。惟有死与辨耳。不死则当辨。未辨则当死。其乌可苟焉而已哉。小邦本缘守义拒贼。罹此丧败。设令终不支撑。自此沦灭犹为死义之鬼。此名未雪则虽快剪深雠。尽复全疆。终是叛君之身。此寡君之所以日夜腐心。直欲搥胸自列于 天陛之下而不可得者也。抑有一说。今日之诬小邦。是不过执一书为罪案。而小邦恪事 天朝之义。是实天下所知。不须烦引他事。就其书而證之。亦足以明其诬。序末揭成化纪元。卷尾书弘治年号。是果不奉正朔乎。于其遣使也书来朝。于其给粮也书赐米。于关白昼死。于国俗书变诈书欺诳。是果尊奉日本乎。且其本纪仍用僭称年号者。只是因其所纪而为之编次。故书之凡例有曰日本纪用其年号。琉球纪用 中国年号云者。即其义已昭昭矣。是果奉日本年号而然乎。其书已经丁赞画呈进。 试取而考之可立辨也。况烧夷墓社。鱼肉生灵八年以来。抗贼者何事。而今反谓之诱倭同犯。 閤下亦既博观前史。古今天下。宁有是乎。虽疮痍沟壑。朝夕死亡。而惟是君亲伦纪。炳然不昧。咸欲凭仗 皇灵。剪灭仇雠。以伸区区之义。而今遽陷于恶逆之境。不惟小邦情事诚可哀怜。抑 天朝
之义。惟有死与辨耳。不死则当辨。未辨则当死。其乌可苟焉而已哉。小邦本缘守义拒贼。罹此丧败。设令终不支撑。自此沦灭犹为死义之鬼。此名未雪则虽快剪深雠。尽复全疆。终是叛君之身。此寡君之所以日夜腐心。直欲搥胸自列于 天陛之下而不可得者也。抑有一说。今日之诬小邦。是不过执一书为罪案。而小邦恪事 天朝之义。是实天下所知。不须烦引他事。就其书而證之。亦足以明其诬。序末揭成化纪元。卷尾书弘治年号。是果不奉正朔乎。于其遣使也书来朝。于其给粮也书赐米。于关白昼死。于国俗书变诈书欺诳。是果尊奉日本乎。且其本纪仍用僭称年号者。只是因其所纪而为之编次。故书之凡例有曰日本纪用其年号。琉球纪用 中国年号云者。即其义已昭昭矣。是果奉日本年号而然乎。其书已经丁赞画呈进。 试取而考之可立辨也。况烧夷墓社。鱼肉生灵八年以来。抗贼者何事。而今反谓之诱倭同犯。 閤下亦既博观前史。古今天下。宁有是乎。虽疮痍沟壑。朝夕死亡。而惟是君亲伦纪。炳然不昧。咸欲凭仗 皇灵。剪灭仇雠。以伸区区之义。而今遽陷于恶逆之境。不惟小邦情事诚可哀怜。抑 天朝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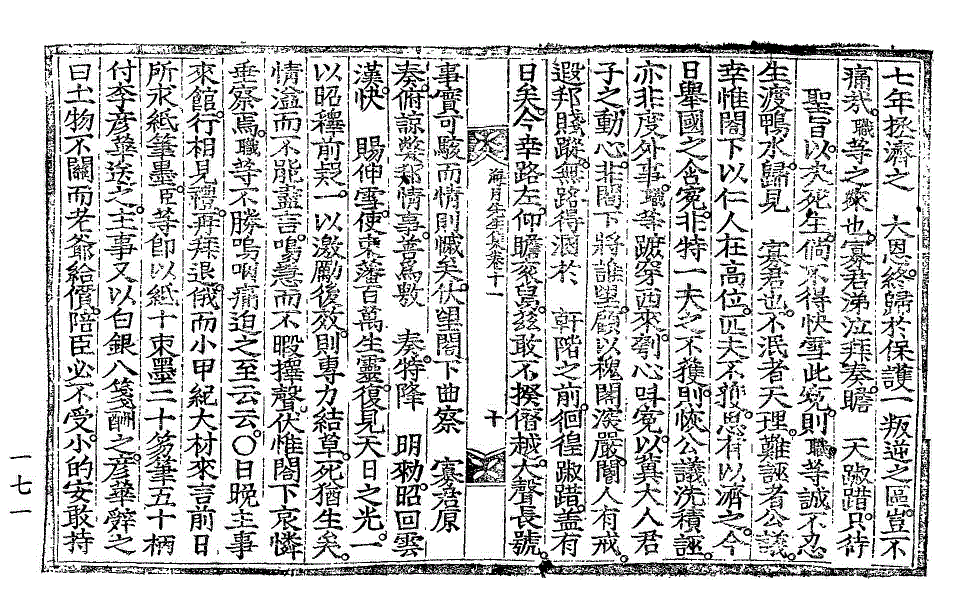 七年拯济之 大恩。终归于保护一叛逆之区。岂不痛哉。职等之来也。寡君涕泣拜奏。瞻 天踧踖。只待 圣旨。以决死生。倘不得快雪此冤。则职等诚不忍生渡鸭水。归见 寡君也。不泯者天理。难诬者公议。幸惟閤下以仁人在高位。匹夫不获。思有以济之。今日举国之含冤。非特一夫之不获。则恢公议洗积诬。亦非度外事。职等蹠穿西来。刳心叫冤。以冀大人君子之动心。非閤下将谁望。顾以槐阁深严。阍人有戒。遐邦贱踪。无路得溷于 轩阶之前。徊徨踧踖。盖有日矣。今幸路左。仰瞻衮舄。玆敢不揆僭越。大声长号。事实可骇而情则戚矣。伏望閤下曲察 寡君原 奏。俯谅弊邦情事。善为敷 奏。特降 明敕。昭回云汉。快 赐伸雪。使东藩百万生灵。复见天日之光。一以昭释前疑。一以激励后效。则专力结草。死犹生矣。情溢而不能尽言。鸣急而不暇择声。伏惟閤下哀怜垂察焉。职等不胜呜咽痛迫之至云云。○日晚主事来馆。行相见礼。再拜退俄而小甲纪大材来言前日所求纸笔墨。臣等即以纸十刺墨二十笏笔五十柄付李彦华送之。主事又以白银八笺酬之。彦华辞之曰土物不关而老爷给价。陪臣必不受。小的安敢持
七年拯济之 大恩。终归于保护一叛逆之区。岂不痛哉。职等之来也。寡君涕泣拜奏。瞻 天踧踖。只待 圣旨。以决死生。倘不得快雪此冤。则职等诚不忍生渡鸭水。归见 寡君也。不泯者天理。难诬者公议。幸惟閤下以仁人在高位。匹夫不获。思有以济之。今日举国之含冤。非特一夫之不获。则恢公议洗积诬。亦非度外事。职等蹠穿西来。刳心叫冤。以冀大人君子之动心。非閤下将谁望。顾以槐阁深严。阍人有戒。遐邦贱踪。无路得溷于 轩阶之前。徊徨踧踖。盖有日矣。今幸路左。仰瞻衮舄。玆敢不揆僭越。大声长号。事实可骇而情则戚矣。伏望閤下曲察 寡君原 奏。俯谅弊邦情事。善为敷 奏。特降 明敕。昭回云汉。快 赐伸雪。使东藩百万生灵。复见天日之光。一以昭释前疑。一以激励后效。则专力结草。死犹生矣。情溢而不能尽言。鸣急而不暇择声。伏惟閤下哀怜垂察焉。职等不胜呜咽痛迫之至云云。○日晚主事来馆。行相见礼。再拜退俄而小甲纪大材来言前日所求纸笔墨。臣等即以纸十刺墨二十笏笔五十柄付李彦华送之。主事又以白银八笺酬之。彦华辞之曰土物不关而老爷给价。陪臣必不受。小的安敢持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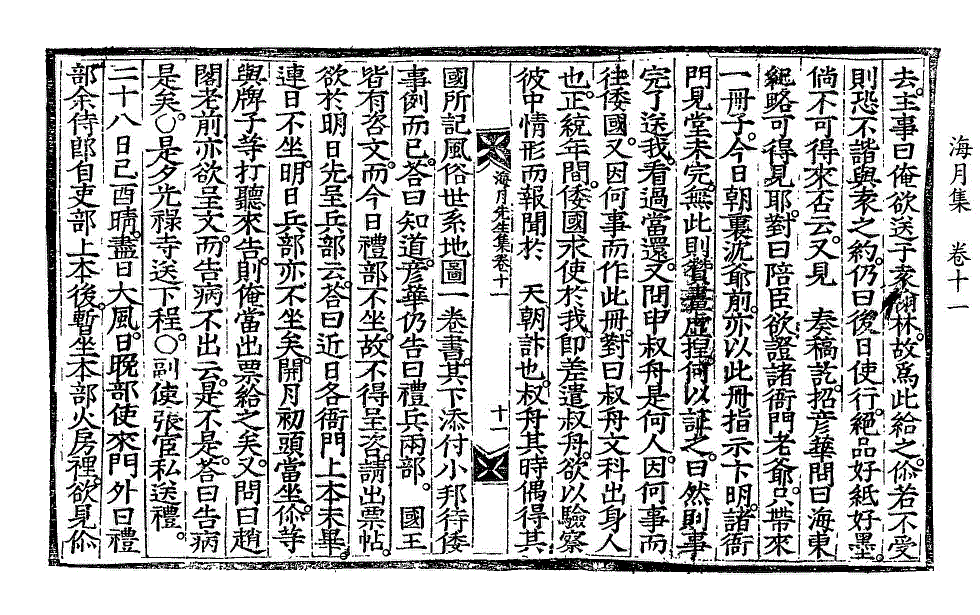 去。主事曰俺欲送于袁翰林。故为此给之。你若不受则恐不谐与袁之约。仍曰后日使行。绝品好纸好墨。倘不可得来否云。又见 奏稿讫。招彦华问曰海东纪略可得见耶。对曰陪臣欲證诸衙门老爷。只带来一册子。今日朝里沈爷前。亦以此册指示卞明。诸衙门见堂未完。无此则赞画虚捏。何以证之。曰然则事完了送我。看过当还。又问申叔舟是何人。因何事而往倭国。又因何事而作此册。对曰叔舟文科出身人也。正统年间。倭国求使于我。即差遣叔舟。欲以验察彼中情形而报闻于 天朝计也。叔舟其时偶得其国所记风俗世系地图一卷书。其下添付小邦待倭事例而已。答曰知道。彦华仍告曰礼兵两部。 国王皆有咨文。而今日礼部不坐。故不得呈咨。请出票帖。欲于明日先呈兵部云。答曰近日各衙门上本末毕。连日不坐。明日兵部亦不坐矣。开月初头当坐。你等与牌子等打听来告。则俺当出票给之矣。又问曰赵阁老前亦欲呈文。而告病不出云。是不是。答曰告病是矣。○是夕光禄寺送下程。○副使张宦私送礼。
去。主事曰俺欲送于袁翰林。故为此给之。你若不受则恐不谐与袁之约。仍曰后日使行。绝品好纸好墨。倘不可得来否云。又见 奏稿讫。招彦华问曰海东纪略可得见耶。对曰陪臣欲證诸衙门老爷。只带来一册子。今日朝里沈爷前。亦以此册指示卞明。诸衙门见堂未完。无此则赞画虚捏。何以证之。曰然则事完了送我。看过当还。又问申叔舟是何人。因何事而往倭国。又因何事而作此册。对曰叔舟文科出身人也。正统年间。倭国求使于我。即差遣叔舟。欲以验察彼中情形而报闻于 天朝计也。叔舟其时偶得其国所记风俗世系地图一卷书。其下添付小邦待倭事例而已。答曰知道。彦华仍告曰礼兵两部。 国王皆有咨文。而今日礼部不坐。故不得呈咨。请出票帖。欲于明日先呈兵部云。答曰近日各衙门上本末毕。连日不坐。明日兵部亦不坐矣。开月初头当坐。你等与牌子等打听来告。则俺当出票给之矣。又问曰赵阁老前亦欲呈文。而告病不出云。是不是。答曰告病是矣。○是夕光禄寺送下程。○副使张宦私送礼。二十八日己酉晴。尽日大风。日晚部使来门外曰礼部余侍郎自吏部上本后。暂坐本部火房里。欲见你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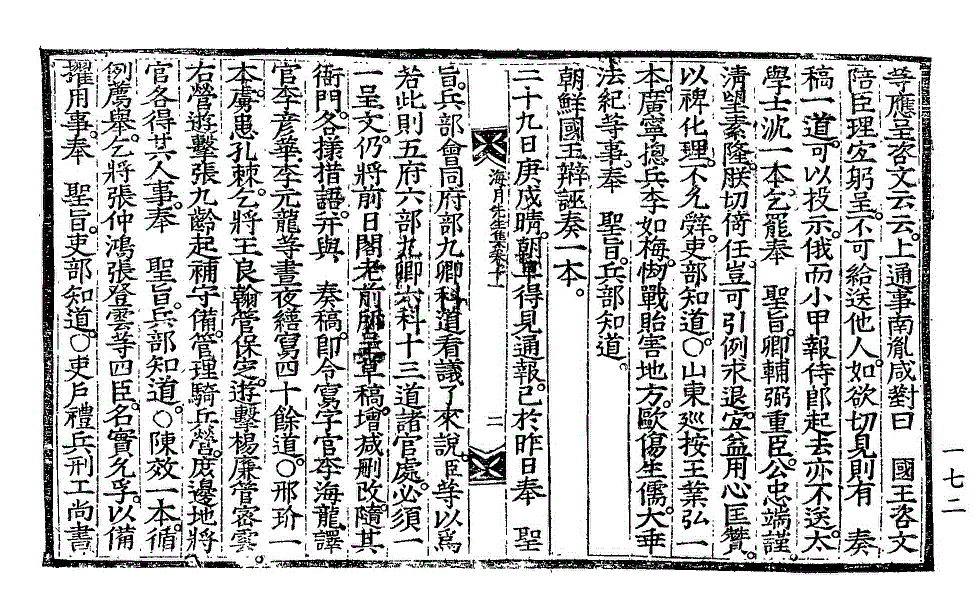 等应呈咨文云云。上通事南胤咸对曰 国王咨文陪臣理宜躬呈。不可给送他人。如欲切见则有 奏稿一道。可以投示。俄而小甲报侍郎起去亦不送。太学士沈一本。乞罢奉 圣旨。卿辅弼重臣。公忠端谨清望素隆。朕切倚任。岂可引例求退。宜益用心匡赞。以裨化理。不允辞。吏部知道。○山东巡按王业弘一本。广宁总兵李如梅。㥘战贻害地方。欧伤生儒。大乖法纪等事。奉 圣旨。兵部知道。
等应呈咨文云云。上通事南胤咸对曰 国王咨文陪臣理宜躬呈。不可给送他人。如欲切见则有 奏稿一道。可以投示。俄而小甲报侍郎起去亦不送。太学士沈一本。乞罢奉 圣旨。卿辅弼重臣。公忠端谨清望素隆。朕切倚任。岂可引例求退。宜益用心匡赞。以裨化理。不允辞。吏部知道。○山东巡按王业弘一本。广宁总兵李如梅。㥘战贻害地方。欧伤生儒。大乖法纪等事。奉 圣旨。兵部知道。朝鲜国王辨诬奏一本。
二十九日庚戌晴。朝早得见通报。已于昨日奉 圣旨。兵部会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议了来说。臣等以为若此则五府六部九卿六科十三道诸官处。必须一一呈文。仍将前日阁老前所呈草稿。增减删改。随其衙门。各样措语。并与 奏稿。即令写字官李海龙,译官李彦华,李元龙等昼夜缮写四十馀道。○邢玠一本。虏患孔棘。乞将王良翰管保定。游击杨廉管密云。右营游击张九龄起补守备。管理骑兵营。庶边地将官各得其人事。奉 圣旨。兵部知道。○陈效一本。循例荐举。乞将张仲鸿,张登云等四臣。名实允孚。以备擢用事。奉 圣旨。吏部知道。○吏户礼兵刑工尚书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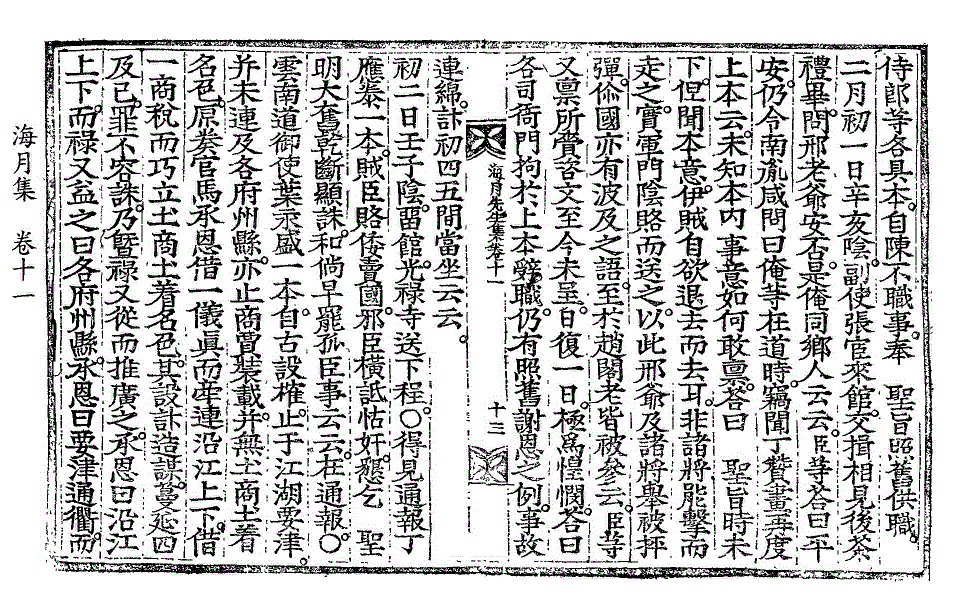 侍郎等各具本。自陈不职事。奉 圣旨照旧供职。
侍郎等各具本。自陈不职事。奉 圣旨照旧供职。[己亥二月]
二月初一日辛亥阴。副使张宦来馆。交揖相见后茶礼毕。问邢老爷安否。是俺同乡人云云。臣等答曰平安。仍令南胤咸问曰俺等在道时。窃闻丁赞画再度上本云。未知本内事意如何敢禀。答曰 圣旨。时未下。但闻本意。伊贼自欲退去而去耳。非诸将能击而走之。实军门阴赂而送之。以此邢爷及诸将举被抨弹。你国亦有波及之语。至于赵阁老皆被参云。臣等又禀所赍咨文至今未呈。日复一日。极为惶悯。答曰各司衙门拘于上本辞职。仍有照旧谢恩之例。事故连绵。计初四五间当坐云云。
初二日壬子阴。留馆。光禄寺送下程。○得见通报丁应泰一本。贼臣赂倭卖国。邪臣横诋怙奸。恳乞 圣明大奋乾断显诛。和倘早罢孤臣事云云。在通报。○云南道御使叶永盛一本。自古设榷。止于江湖要津。并未连及各府州县。亦止商贾装载。并无土商土着名色。原奏官马承恩借一仪真而牵连沿江上下。借一商税而巧立土商土着名色。其设计造谋。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诛。乃暨禄又从而推广之。承恩曰沿江上下。而禄又益之曰各府州县。承恩曰要津通衢。而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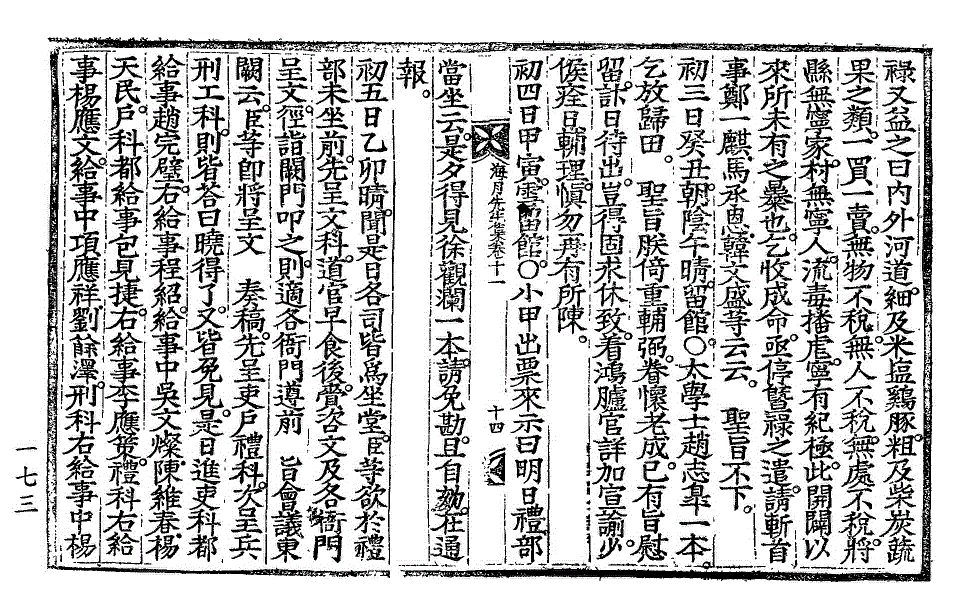 禄又益之曰内外河道。细及米盐鸡豚。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人不税。无处不税。将县无宁家。村无宁人。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乞收成命。亟停暨禄之遣。请斩首事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云云。 圣旨不下。
禄又益之曰内外河道。细及米盐鸡豚。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人不税。无处不税。将县无宁家。村无宁人。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乞收成命。亟停暨禄之遣。请斩首事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云云。 圣旨不下。初三日癸丑。朝阴午晴。留馆。○太学士赵志皋一本乞放归田。 圣旨朕倚重辅弼。眷怀老成。已有旨慰留。计日待出。岂得固求休致。着鸿胪官详加宣谕。少候痊日辅理。慎勿再有所陈。
初四日甲寅。雪留馆。○小甲出票来示曰明日礼部当坐云。是夕得见徐观澜一本。请免勘。且自劾。在通报。
初五日乙卯晴。闻是日各司皆为坐堂。臣等欲于礼部未坐前。先呈文科。道官早食后。赍咨文及各衙门呈文。径诣阙门叩之。则适各衙门遵前 旨会议东阙云。臣等即将呈文 奏稿。先呈吏户礼科。次呈兵刑工科。则皆答曰晓得了。又皆免见。是日进吏科都给事赵完璧。右给事程绍。给事中吴文灿,陈维春,杨天民。户科都给事包见捷。右给事李应策。礼科右给事杨应文。给事中项应祥,刘馀泽。刑科右给事中杨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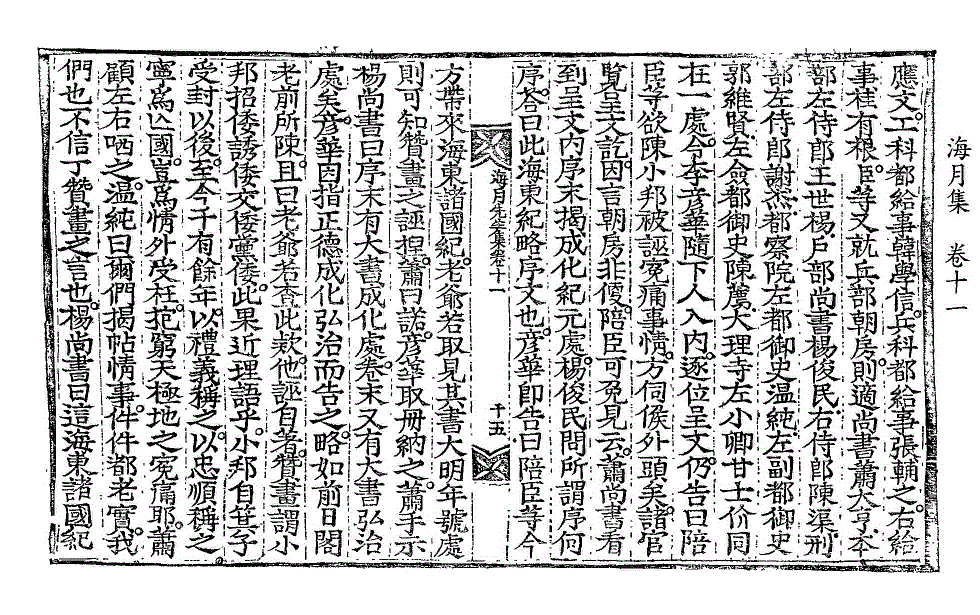 应文。工科都给事韩学信。兵科都给事张辅之。右给事桂有根。臣等又就兵部朝房。则适尚书萧大亨,本部左侍郎王世杨,户部尚书杨俊民,右侍郎陈渠,刑部左侍郎谢杰,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左副都御史郭维贤,左佥都御史陈荐,大理寺左小卿甘士价同在一处。令李彦华随下人入内。逐位呈文。仍告曰陪臣等欲陈小邦被诬冤痛事情。方伺候外头矣。诸官览呈文讫。因言朝房非便。陪臣可免见云。萧尚书看到呈文内序末揭成化纪元处。杨俊民问所谓序何序。答曰此海东纪略序文也。彦华即告曰陪臣等今方带来海东诸国纪。老爷若取见其书大明年号处则可知赞画之诬捏。萧曰诺。彦华取册纳之。萧手示杨尚书曰序末有大书成化处。卷末又有大书弘治处矣。彦华因指正德成化弘治而告之。略如前日阁老前所陈。且曰老爷若查此款。他诬自著。赞画谓小邦招倭诱倭交倭党倭。此果近理语乎。小邦自箕子受封以后。至今千有馀年。以礼义称之。以忠顺称之。宁为亡国。岂为情外受枉。抱穷天极地之冤痛耶。萧顾左右哂之。温纯曰尔们揭帖情事。件件都老实。我们也不信丁赞画之言也。杨尚书曰这海东诸国纪
应文。工科都给事韩学信。兵科都给事张辅之。右给事桂有根。臣等又就兵部朝房。则适尚书萧大亨,本部左侍郎王世杨,户部尚书杨俊民,右侍郎陈渠,刑部左侍郎谢杰,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左副都御史郭维贤,左佥都御史陈荐,大理寺左小卿甘士价同在一处。令李彦华随下人入内。逐位呈文。仍告曰陪臣等欲陈小邦被诬冤痛事情。方伺候外头矣。诸官览呈文讫。因言朝房非便。陪臣可免见云。萧尚书看到呈文内序末揭成化纪元处。杨俊民问所谓序何序。答曰此海东纪略序文也。彦华即告曰陪臣等今方带来海东诸国纪。老爷若取见其书大明年号处则可知赞画之诬捏。萧曰诺。彦华取册纳之。萧手示杨尚书曰序末有大书成化处。卷末又有大书弘治处矣。彦华因指正德成化弘治而告之。略如前日阁老前所陈。且曰老爷若查此款。他诬自著。赞画谓小邦招倭诱倭交倭党倭。此果近理语乎。小邦自箕子受封以后。至今千有馀年。以礼义称之。以忠顺称之。宁为亡国。岂为情外受枉。抱穷天极地之冤痛耶。萧顾左右哂之。温纯曰尔们揭帖情事。件件都老实。我们也不信丁赞画之言也。杨尚书曰这海东诸国纪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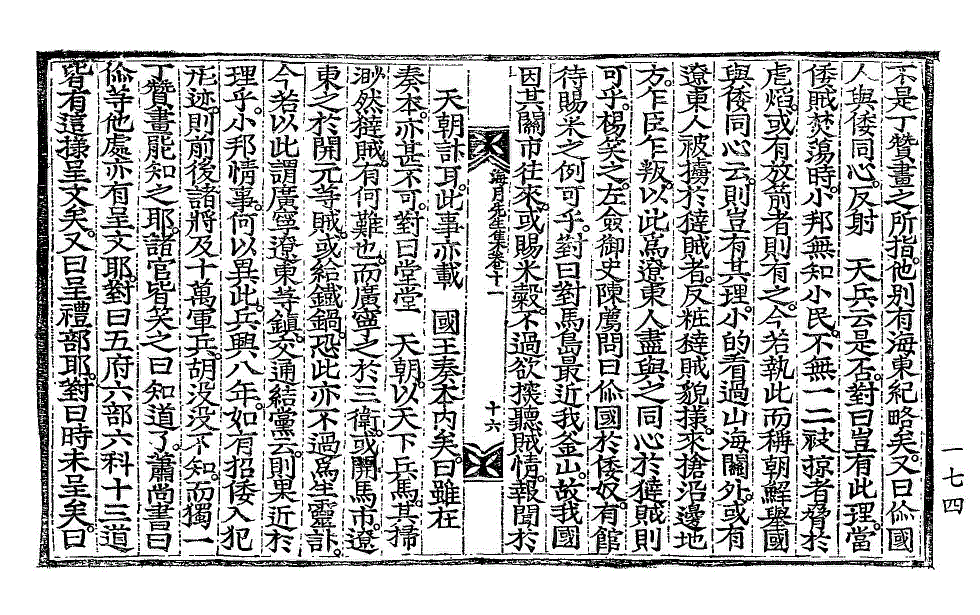 不是丁赞画之所指。他别有海东纪略矣。又曰你国人与倭同心。反射 天兵云是否。对曰岂有此理。当倭贼焚荡时。小邦无知小民。不无一二被掠者胁于虐焰。或有放箭者则有之。今若执此而称朝鲜举国与倭同心云。则岂有其理。小的看过山海关外。或有辽东人被掳于獭贼者。反妆獭贼貌样。来抢沿边地方。乍臣乍叛。以此为辽东人尽与之同心于獭贼则可乎。杨笑之。左佥御史陈荐问曰你国于倭奴。有馆待赐米之例可乎。对曰对马岛最近我釜山。故我国因其关市往来。或赐米谷。不过欲探听贼情。报闻于 天朝计耳。此事亦载 国王奏本内矣。曰虽在 奏本。亦甚不可。对曰堂堂 天朝。以天下兵马。其扫渺然獭贼。有何难也。而广宁之于三卫。或开马市。辽东之于开元等贼。或给铁锅。恐此亦不过为生灵计。今若以此谓广宁辽东等镇。交通结党云。则果近于理乎。小邦情事。何以异此兵兴八年。如有招倭入犯形迹。则前后诸将及十万军兵。胡没没不知。而独一丁赞画能知之耶。诸官皆笑之曰知道了。萧尚书曰你等他处亦有呈文耶。对曰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皆有这样呈文矣。又曰呈礼部耶。对曰时未呈矣。曰
不是丁赞画之所指。他别有海东纪略矣。又曰你国人与倭同心。反射 天兵云是否。对曰岂有此理。当倭贼焚荡时。小邦无知小民。不无一二被掠者胁于虐焰。或有放箭者则有之。今若执此而称朝鲜举国与倭同心云。则岂有其理。小的看过山海关外。或有辽东人被掳于獭贼者。反妆獭贼貌样。来抢沿边地方。乍臣乍叛。以此为辽东人尽与之同心于獭贼则可乎。杨笑之。左佥御史陈荐问曰你国于倭奴。有馆待赐米之例可乎。对曰对马岛最近我釜山。故我国因其关市往来。或赐米谷。不过欲探听贼情。报闻于 天朝计耳。此事亦载 国王奏本内矣。曰虽在 奏本。亦甚不可。对曰堂堂 天朝。以天下兵马。其扫渺然獭贼。有何难也。而广宁之于三卫。或开马市。辽东之于开元等贼。或给铁锅。恐此亦不过为生灵计。今若以此谓广宁辽东等镇。交通结党云。则果近于理乎。小邦情事。何以异此兵兴八年。如有招倭入犯形迹。则前后诸将及十万军兵。胡没没不知。而独一丁赞画能知之耶。诸官皆笑之曰知道了。萧尚书曰你等他处亦有呈文耶。对曰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皆有这样呈文矣。又曰呈礼部耶。对曰时未呈矣。曰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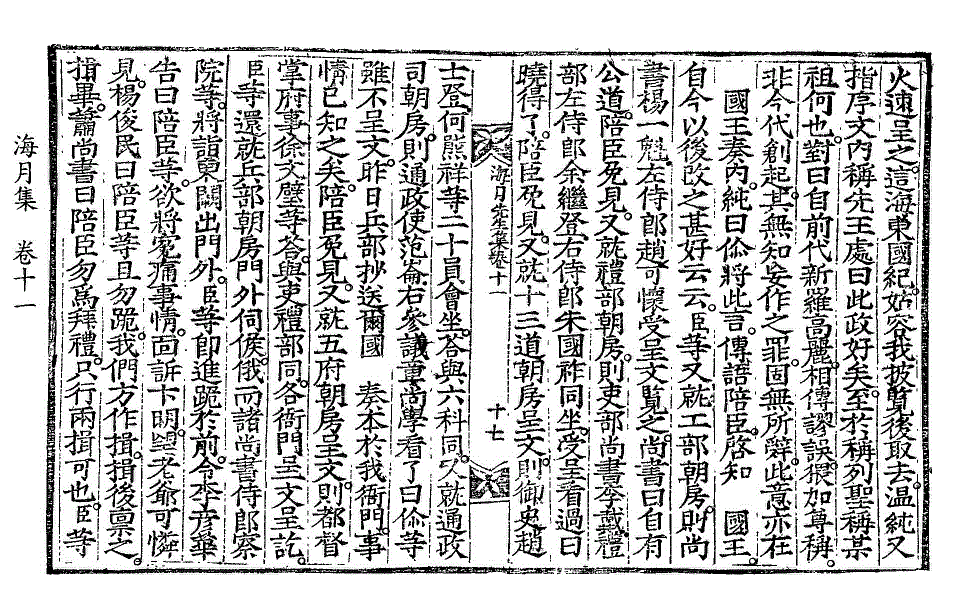 火速呈之。这海东国纪。姑容我披览后取去。温纯又指序文内称先王处曰此政好矣。至于称列圣称某祖何也。对曰自前代新罗高丽。相传谬误。猥加尊称。非今代创起。其无知妄作之罪。固无所辞。此意亦在 国王奏内。纯曰你将此言。传语陪臣。启知 国王。自今以后改之甚好云云。臣等又就工部朝房。则尚书杨一魁,左侍郎赵可怀受呈文览之。尚书曰自有公道。陪臣免见。又就礼部朝房。则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左侍郎余继登,右侍郎朱国祚同坐。受呈看过曰晓得了。陪臣免见。又就十三道朝房呈文。则御史赵士登,何熊祥等二十员会坐。答与六科同。又就通政司朝房。则通政使范崙,右参议章尚学看了。曰你等虽不呈文。昨日兵部抄送尔国 奏本于我衙门。事情已知之矣。陪臣免见。又就五府朝房呈文。则都督掌府事徐文璧等答。与吏礼部同。各衙门呈文呈讫。臣等还就丘部朝房门外伺候。俄而诸尚书侍郎察院等。将诣东阙出门外。臣等即进跪于前。令李彦华告曰陪臣等。欲将冤痛事情。面诉卞明。望老爷可怜见。杨俊民曰陪臣等且勿跪。我们方作揖。揖后禀之。揖毕。萧尚书曰陪臣勿为拜礼。只行两揖可也。臣等
火速呈之。这海东国纪。姑容我披览后取去。温纯又指序文内称先王处曰此政好矣。至于称列圣称某祖何也。对曰自前代新罗高丽。相传谬误。猥加尊称。非今代创起。其无知妄作之罪。固无所辞。此意亦在 国王奏内。纯曰你将此言。传语陪臣。启知 国王。自今以后改之甚好云云。臣等又就工部朝房。则尚书杨一魁,左侍郎赵可怀受呈文览之。尚书曰自有公道。陪臣免见。又就礼部朝房。则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左侍郎余继登,右侍郎朱国祚同坐。受呈看过曰晓得了。陪臣免见。又就十三道朝房呈文。则御史赵士登,何熊祥等二十员会坐。答与六科同。又就通政司朝房。则通政使范崙,右参议章尚学看了。曰你等虽不呈文。昨日兵部抄送尔国 奏本于我衙门。事情已知之矣。陪臣免见。又就五府朝房呈文。则都督掌府事徐文璧等答。与吏礼部同。各衙门呈文呈讫。臣等还就丘部朝房门外伺候。俄而诸尚书侍郎察院等。将诣东阙出门外。臣等即进跪于前。令李彦华告曰陪臣等。欲将冤痛事情。面诉卞明。望老爷可怜见。杨俊民曰陪臣等且勿跪。我们方作揖。揖后禀之。揖毕。萧尚书曰陪臣勿为拜礼。只行两揖可也。臣等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5L 页
 即起两揖还跪。令李彦华告曰自古国家灭亡。代或有之。而君臣伦纪。不容一日泯灭。苟得罪于此。则将何以立于天地间乎。千万古以来。未有如这们冤痛底事。适闻今日将会议。望老爷曲加怜察。特许昭雪。以慰举国君臣上下冤痛之情。萧尚书于众中显有喜闻之色。臣等每一开话。尚书辄顾左右诸老爷诸官曰陪臣起来。你国事情。尽知得了。萧尚书又曰我们已见呈文。陪臣可即去吏礼部面禀。臣等再往礼部朝房门外。则吏礼部官。与萧尚书以下诸官。于门外交揖。分左右列立。臣等趋进阶下。欲有所陈。余侍郎继登色甚不平。麾使退去。臣等不敢开说而退。仍往礼部伺候。俄而余朱两侍郎自会议所来坐堂。臣等行见堂礼。再拜讫仍跪呈咨文。又呈免宴呈文。令李彦华告曰今日陪臣等。于阙内朝房呈文。固知事体非便。而为缘情理切痛。冒昧渎扰。惶恐惶恐。余侍郎曰知道起来。臣等即退来。○其呈文曰陪臣某等。谨呈为免宴事。窃照 锡宴一节。所以宠劳远人。礼甚盛也恩至渥也。第惟弊邦君臣。积年薪胆。虽有支撑一息之存。亦非临食下咽之时。前后贱价节。将前项事情。累次呈蒙免例。况今横被恶逆之名。至有覆
即起两揖还跪。令李彦华告曰自古国家灭亡。代或有之。而君臣伦纪。不容一日泯灭。苟得罪于此。则将何以立于天地间乎。千万古以来。未有如这们冤痛底事。适闻今日将会议。望老爷曲加怜察。特许昭雪。以慰举国君臣上下冤痛之情。萧尚书于众中显有喜闻之色。臣等每一开话。尚书辄顾左右诸老爷诸官曰陪臣起来。你国事情。尽知得了。萧尚书又曰我们已见呈文。陪臣可即去吏礼部面禀。臣等再往礼部朝房门外。则吏礼部官。与萧尚书以下诸官。于门外交揖。分左右列立。臣等趋进阶下。欲有所陈。余侍郎继登色甚不平。麾使退去。臣等不敢开说而退。仍往礼部伺候。俄而余朱两侍郎自会议所来坐堂。臣等行见堂礼。再拜讫仍跪呈咨文。又呈免宴呈文。令李彦华告曰今日陪臣等。于阙内朝房呈文。固知事体非便。而为缘情理切痛。冒昧渎扰。惶恐惶恐。余侍郎曰知道起来。臣等即退来。○其呈文曰陪臣某等。谨呈为免宴事。窃照 锡宴一节。所以宠劳远人。礼甚盛也恩至渥也。第惟弊邦君臣。积年薪胆。虽有支撑一息之存。亦非临食下咽之时。前后贱价节。将前项事情。累次呈蒙免例。况今横被恶逆之名。至有覆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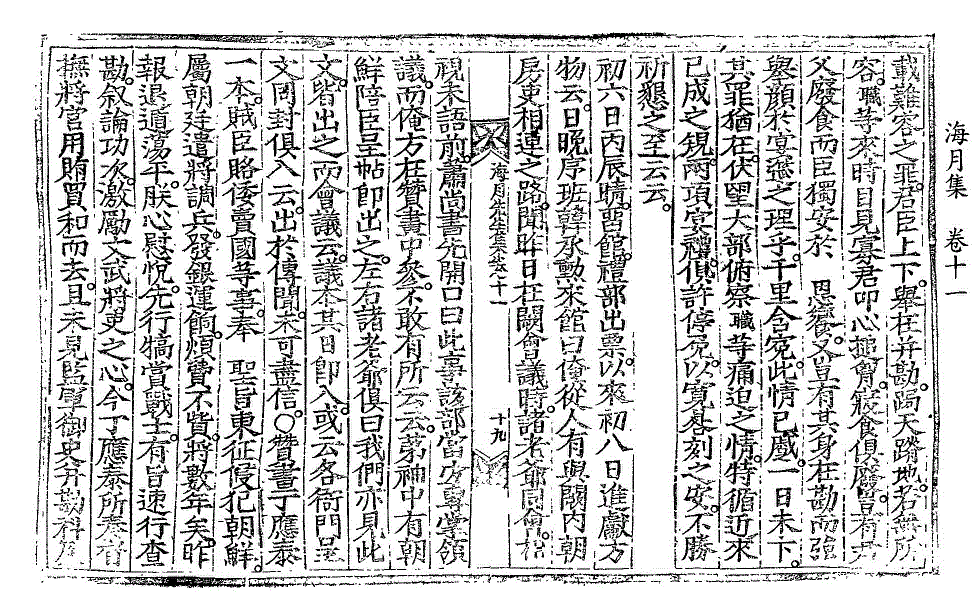 载难容之罪。君臣上下。举在并勘。跼天蹐地。若无所容。职等来时目见寡君叩心搥胸。寝食俱废。岂有君父废食而臣独安于 恩飨。又岂有其身在勘而强举颜于宴筵之理乎。千里含冤。此情已蹙。一日未下其罪犹在。伏望大部俯察职等痛迫之情。特循近来已成之规。两项宴礼。俱许停免。以宽晷刻之安。不胜祈恳之至云云。
载难容之罪。君臣上下。举在并勘。跼天蹐地。若无所容。职等来时目见寡君叩心搥胸。寝食俱废。岂有君父废食而臣独安于 恩飨。又岂有其身在勘而强举颜于宴筵之理乎。千里含冤。此情已蹙。一日未下其罪犹在。伏望大部俯察职等痛迫之情。特循近来已成之规。两项宴礼。俱许停免。以宽晷刻之安。不胜祈恳之至云云。初六日丙辰晴。留馆。礼部出票。以来初八日进献方物云。日晚序班韩承勋来馆曰俺从人有与阙内朝房吏相连之路。闻昨日在阙会议时。诸老爷同会。相视未语前。萧尚书先开口曰此事该部当宜专掌领议。而俺方在赞画中参。不敢有所云云。第袖中有朝鲜陪臣呈帖即出之。左右诸老爷俱曰我们亦见此文。皆出之而会议云。议本其日即入。或云各衙门呈文同封俱入云。出于传闻。未可尽信。○赞画丁应泰一本。贼臣赂倭卖国等事。奉 圣旨东征侵犯朝鲜。属朝廷遣将调兵。发银运饷。烦费不赀。将数年矣。昨报退遁荡平。朕心慰悦。先行犒赏战士。有旨速行查勘。叙论功次。激励文武将吏之心。今丁应泰所奏督抚将官用贿买和而去。且未见监军御史并勘科及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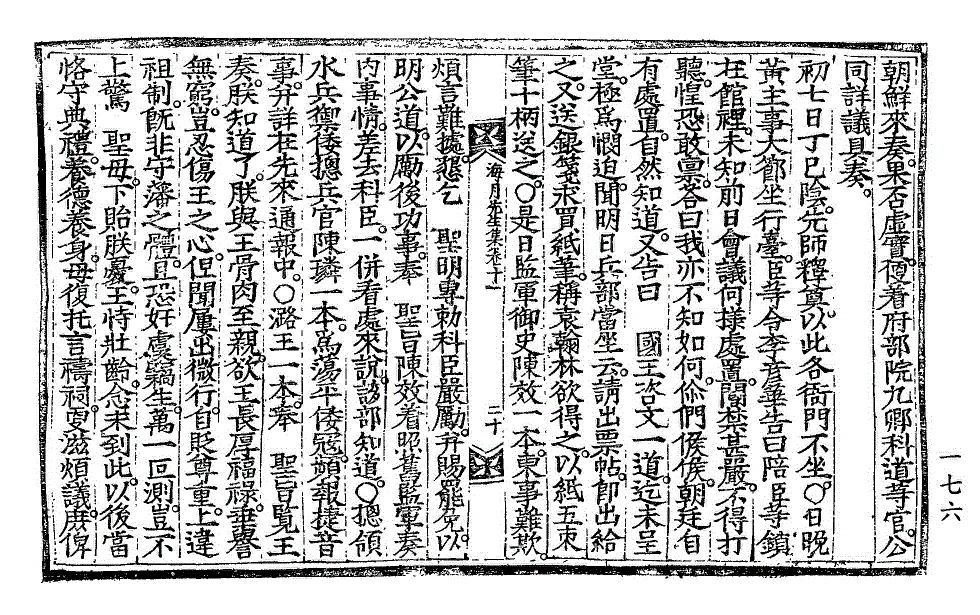 朝鲜来奏。果否虚实。便着府部院九卿科道等官。公同详议具奏。
朝鲜来奏。果否虚实。便着府部院九卿科道等官。公同详议具奏。初七日丁巳阴。先师释奠。以此各衙门不坐。○日晚黄主事大节坐行台。臣等令李彦华告曰陪臣等锁在馆里。未知前日会议何样处置。阍禁甚严。不得打听。惶恐敢禀。答曰我亦不知如何。你们候候。朝廷自有处置。自然知道。又告曰 国王咨文一道。迄未呈堂。极为悯迫。闻明日兵部当坐云。请出票帖。即出给之。又送银笺求买纸笔。称袁翰林欲得之。以纸五束笔十柄送之。○是日监军御史陈效一本。东事难欺。烦言难据。恳乞 圣明专敕科臣严励。并赐罢免。以明公道。以励后功事。奉 圣旨。陈效着照旧监军奏内事情。差去科臣。一并看处来说。该部知道。○总领水兵御倭总兵官陈璘一本。为荡平倭寇。频报捷音事。并详在先来通报中。○潞王一本。奉 圣旨。览王奏。朕知道了。朕与王骨肉至亲。欲王长厚福禄。垂誉无穷。岂忍伤玉之心。但闻屡出微行。自贬尊重。上违祖制。既非守藩之体。且恐奸虞窃生。万一叵测。岂不上惊 圣母。下贻朕忧。王恃壮龄。念未到此。以后当恪守典礼。养德养身。毋复托言祷祠。更滋烦议。庶俾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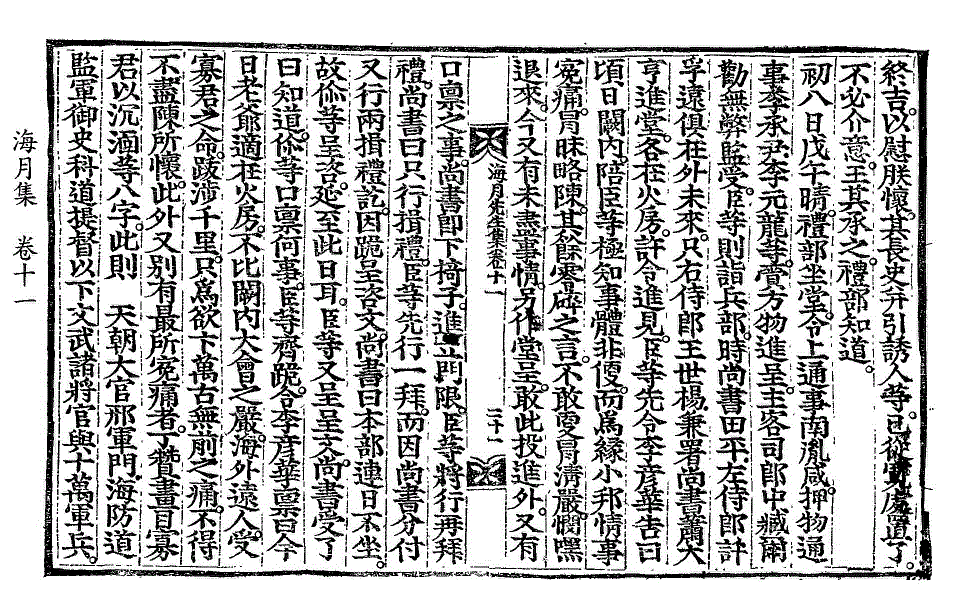 终吉。以慰朕怀。其长史并引诱人等。已从宽处置了。不必介意。王其承之。礼部知道。
终吉。以慰朕怀。其长史并引诱人等。已从宽处置了。不必介意。王其承之。礼部知道。初八日戊午晴。礼部坐堂。令上通事南胤咸。押物通事李承尹,李元龙等。赍方物进呈。主客司郎中臧尔劝无弊监受。臣等则诣兵部。时尚书田平,左侍郎许孚远俱在外未来。只右侍郎王世杨,兼署尚书萧大亨进堂。各在火房。许令进见。臣等先令李彦华告曰顷日阙内。陪臣等极知事体非便。而为缘小邦情事冤痛。冒昧略陈。其馀零碎之言。不敢更冒清严。悯嘿退来。今又有未尽事情。另作堂呈。敢此投进外。又有口禀之事。尚书即下掎子。进立门限。臣等将行再拜礼。尚书曰只行揖礼。臣等先行一拜。而因尚书分付又行两揖礼讫。因跪呈咨文。尚书曰本部连日不坐。故你等呈咨。延至此日耳。臣等又呈呈文。尚书受了。曰知道。你等口禀何事。臣等齐跪。合李彦华禀曰今日老爷适在火房。不比阙内大会之严。海外远人。受寡君之命。跋涉千里。只为欲卞万古无前之痛。不得不尽陈所怀。此外又别有最所冤痛者。丁赞画目寡君以沈湎等八字。此则 天朝大官邢军门,海防道监军御史科道提督以下文武诸将官与十万军兵。
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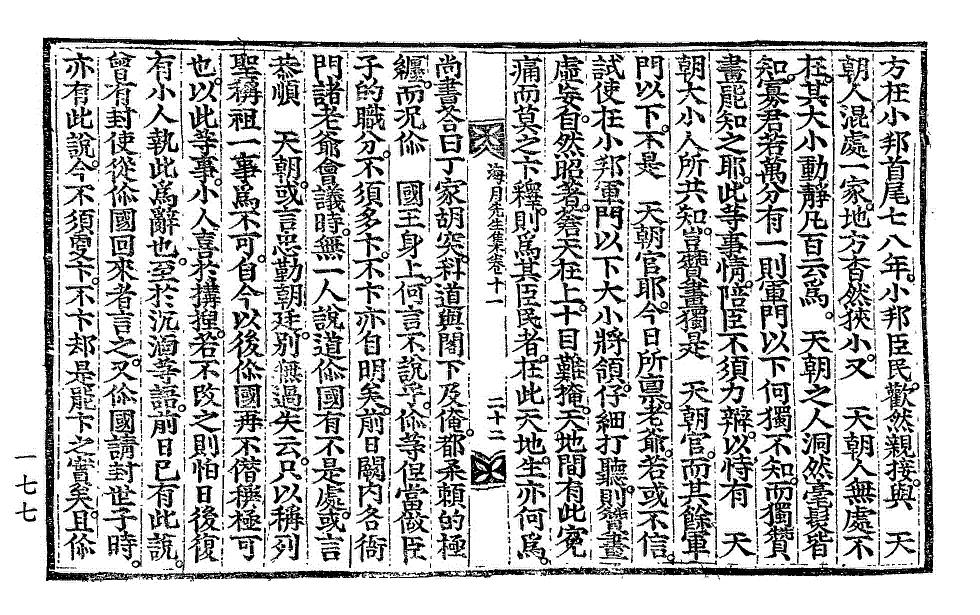 方在小邦首尾七八年。小邦臣民。欢然亲接。与 天朝人混处一家。地方杳然狭小。又 天朝人无处不在。其大小动静凡百云为。 天朝之人洞然毫发皆知。寡君若万分有一则军门以下何独不知。而独赞画罢知之耶。此等事情。陪臣不须力辨。以恃有 天朝大小人所共知。岂赞画独是 天朝官。而其馀军门以下。不是 天朝官耶。今日所禀。老爷。若或不信。试使在小邦军门以下大小将领。仔细打听。则赞画虚妄。自然昭著。苍天在上。十目难掩。天地间有此冤痛而莫之卞释。则为其臣民者。在此天地。生亦何为。尚书答曰丁家胡突。科道与阁下及俺。都条赖的极缠。而况你 国王身上。何言不说乎。你等但当做臣子的职分。不须多卞。不卞亦自明矣。前日阙内各衙门诸老爷会议时。无一人说道你国有不是处。或言恭顺 天朝。或言忠勤朝廷。别无过失云。只以称列圣称祖一事为不可。自今以后你国再不僭称极可也。以此等事。小人喜于搆捏。若不改之则怕日后复有小人执此为辞也。至于沉湎等语。前日已有此说。曾有封使从你国回来者言之。又你国请封世子时。亦有此说。今不须更卞。不卞却是能卞之实矣。且你
方在小邦首尾七八年。小邦臣民。欢然亲接。与 天朝人混处一家。地方杳然狭小。又 天朝人无处不在。其大小动静凡百云为。 天朝之人洞然毫发皆知。寡君若万分有一则军门以下何独不知。而独赞画罢知之耶。此等事情。陪臣不须力辨。以恃有 天朝大小人所共知。岂赞画独是 天朝官。而其馀军门以下。不是 天朝官耶。今日所禀。老爷。若或不信。试使在小邦军门以下大小将领。仔细打听。则赞画虚妄。自然昭著。苍天在上。十目难掩。天地间有此冤痛而莫之卞释。则为其臣民者。在此天地。生亦何为。尚书答曰丁家胡突。科道与阁下及俺。都条赖的极缠。而况你 国王身上。何言不说乎。你等但当做臣子的职分。不须多卞。不卞亦自明矣。前日阙内各衙门诸老爷会议时。无一人说道你国有不是处。或言恭顺 天朝。或言忠勤朝廷。别无过失云。只以称列圣称祖一事为不可。自今以后你国再不僭称极可也。以此等事。小人喜于搆捏。若不改之则怕日后复有小人执此为辞也。至于沉湎等语。前日已有此说。曾有封使从你国回来者言之。又你国请封世子时。亦有此说。今不须更卞。不卞却是能卞之实矣。且你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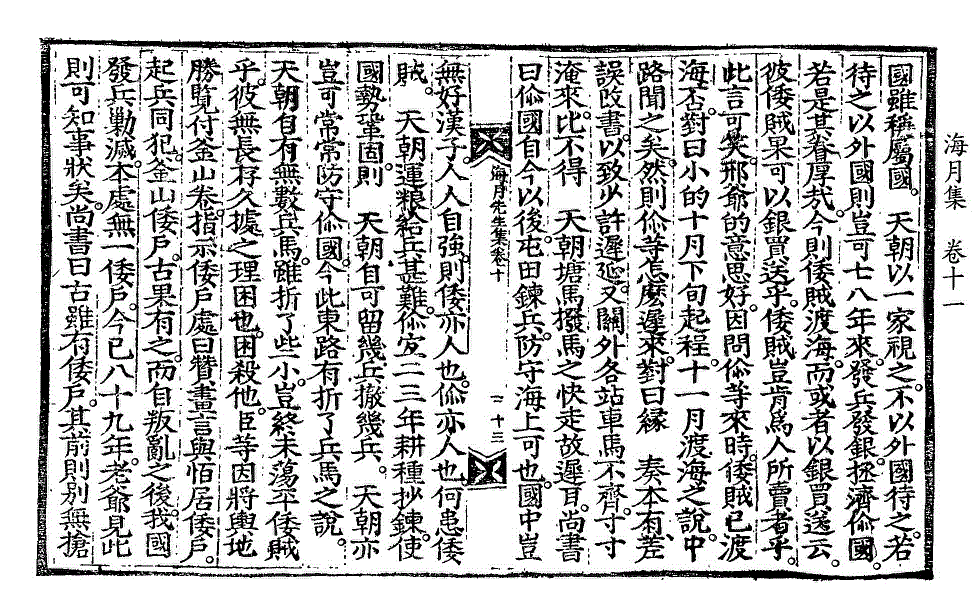 国虽称属国。 天朝以一家视之。不以外国待之。若待之以外国则岂可七八年来。发兵发银。拯济你国。若是其眷厚哉。今则倭贼渡海。而或者以银买送云。彼倭贼果可以银买送乎。倭贼岂肯为人所卖者乎。此言可笑。邢爷的意思好。因问你等来时。倭贼已渡海否。对曰小的十月下旬起程。十一月渡海之说。中路闻之矣。然则你等怎么迟来。对曰缘 奏本有差误改书。以致少许迟延。又关外各站车马不齐。寸寸淹来。比不得 天朝塘马拨马之快走故迟耳。尚书曰你国自今以后。屯田鍊兵。防守海上可也。国中岂无好汉子。人人自强。则倭亦人也。你亦人也。何患倭贼。 天朝运粮给兵甚难。你宜二三年耕种抄鍊。使国势巩固。则 天朝自可留几兵撤几兵。 天朝亦岂可常常防守你国。今此东路有折了兵马之说。 天朝自有无数兵马。虽折了些小。岂终未荡平倭贼乎。彼无长存久据之理困也。困杀他。臣等因将舆地胜览付釜山卷。指示倭户处曰赞画言与恒居倭户。起兵同犯。釜山倭户。古果有之。而自叛乱之后。我国发兵剿灭。本处无一倭户。今已八十九年。老爷见此则可知事状矣。尚书曰古虽有倭户。其前则别无抢
国虽称属国。 天朝以一家视之。不以外国待之。若待之以外国则岂可七八年来。发兵发银。拯济你国。若是其眷厚哉。今则倭贼渡海。而或者以银买送云。彼倭贼果可以银买送乎。倭贼岂肯为人所卖者乎。此言可笑。邢爷的意思好。因问你等来时。倭贼已渡海否。对曰小的十月下旬起程。十一月渡海之说。中路闻之矣。然则你等怎么迟来。对曰缘 奏本有差误改书。以致少许迟延。又关外各站车马不齐。寸寸淹来。比不得 天朝塘马拨马之快走故迟耳。尚书曰你国自今以后。屯田鍊兵。防守海上可也。国中岂无好汉子。人人自强。则倭亦人也。你亦人也。何患倭贼。 天朝运粮给兵甚难。你宜二三年耕种抄鍊。使国势巩固。则 天朝自可留几兵撤几兵。 天朝亦岂可常常防守你国。今此东路有折了兵马之说。 天朝自有无数兵马。虽折了些小。岂终未荡平倭贼乎。彼无长存久据之理困也。困杀他。臣等因将舆地胜览付釜山卷。指示倭户处曰赞画言与恒居倭户。起兵同犯。釜山倭户。古果有之。而自叛乱之后。我国发兵剿灭。本处无一倭户。今已八十九年。老爷见此则可知事状矣。尚书曰古虽有倭户。其前则别无抢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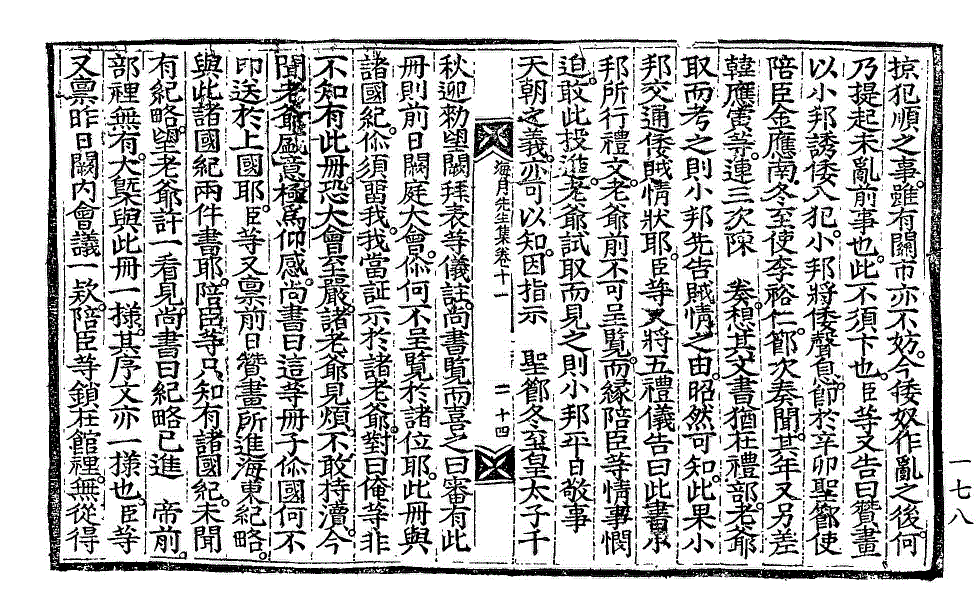 掠犯顺之事。虽有关市亦不妨。今倭奴作乱之后。何乃提起未乱前事也。此不须卞也。臣等又告曰赞画以小邦诱倭入犯。小邦将倭声息。即于辛卯圣节使陪臣金应南,冬至使李裕仁。节次奏闻。其年又另差韩应寅等。连三次陈 奏。想其文书犹在礼部。老爷取而考之则小邦先告贼情之由。昭然可知。此果小邦交通倭贼情状耶。臣等又将五礼仪告曰此书小邦所行礼文。老爷前不可呈览。而缘陪臣等情事悯迫。敢此投进。老爷试取而见之则小邦平日敬事 天朝之义。亦可以知。因指示 圣节冬至皇太子千秋迎敕望阙拜表等仪注。尚书览而喜之曰审有此册则前日阙庭大会。你何不呈览于诸位耶。此册与诸国纪。你须留我。我当证示于诸老爷。对曰俺等非不知有此册。恐大会至严。诸老爷见烦。不敢持渎今闻老爷盛意。极为仰感。尚书曰这等册子你国何不印送于上国耶。臣等又禀前日赞画所进海东纪略。与此诸国纪两件书耶。陪臣等只知有诸国纪。未闻有纪略。望老爷许一看见。尚书曰纪略已进 帝前。部里无有。大概与此册一样。其序文亦一样也。臣等又禀昨日阙内会议一款。陪臣等锁在馆里。无从得
掠犯顺之事。虽有关市亦不妨。今倭奴作乱之后。何乃提起未乱前事也。此不须卞也。臣等又告曰赞画以小邦诱倭入犯。小邦将倭声息。即于辛卯圣节使陪臣金应南,冬至使李裕仁。节次奏闻。其年又另差韩应寅等。连三次陈 奏。想其文书犹在礼部。老爷取而考之则小邦先告贼情之由。昭然可知。此果小邦交通倭贼情状耶。臣等又将五礼仪告曰此书小邦所行礼文。老爷前不可呈览。而缘陪臣等情事悯迫。敢此投进。老爷试取而见之则小邦平日敬事 天朝之义。亦可以知。因指示 圣节冬至皇太子千秋迎敕望阙拜表等仪注。尚书览而喜之曰审有此册则前日阙庭大会。你何不呈览于诸位耶。此册与诸国纪。你须留我。我当证示于诸老爷。对曰俺等非不知有此册。恐大会至严。诸老爷见烦。不敢持渎今闻老爷盛意。极为仰感。尚书曰这等册子你国何不印送于上国耶。臣等又禀前日赞画所进海东纪略。与此诸国纪两件书耶。陪臣等只知有诸国纪。未闻有纪略。望老爷许一看见。尚书曰纪略已进 帝前。部里无有。大概与此册一样。其序文亦一样也。臣等又禀昨日阙内会议一款。陪臣等锁在馆里。无从得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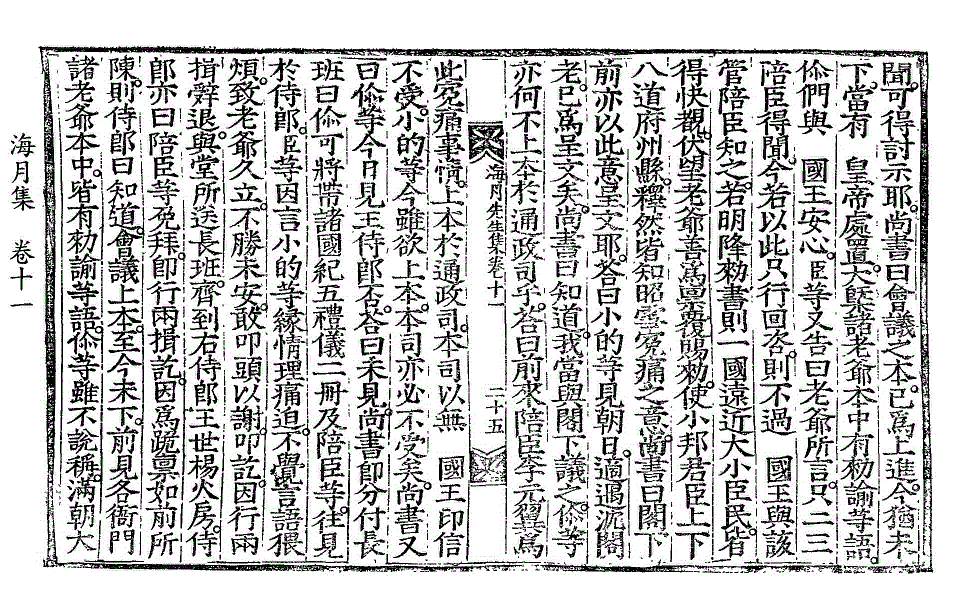 闻。可得讨示耶。尚书曰会议之本。已为上进。今犹未下。当有 皇帝处置。大槩诸老爷本中有敕谕等语。你们与 国王安心。臣等又告曰老爷所言。只二三陪臣得闻。今若以此只行回咨。则不过 国王与该管陪臣知之。若明降敕书则一国远近大小臣民。皆得快睹。伏望老爷善为禀覆赐敕。使小邦君臣上下八道府州县。释然皆知昭雪冤痛之意。尚书曰阁下前亦以此意呈文耶。答曰小的等见朝日。适遇沈阁老。已为呈文矣。尚书曰知道。我当与阁下议之。你等亦何不上本于通政司乎。答曰前来陪臣李元翼为此冤痛事情。上本于通政司。本司以无 国王印信不受。小的等今虽欲上本。本司亦必不受矣。尚书又曰你等今日见王侍郎否。答曰未见。尚书即分付长班曰你可将带诸国纪五礼仪二册及陪臣等。往见于侍郎。臣等因言小的等缘情理痛迫。不觉言语猥烦。致老爷久立。不胜未安。敢叩头以谢。叩讫。因行两揖辞退。与堂所送长班。齐到右侍郎王世杨火房。侍郎亦曰陪臣等免拜。即行两揖讫。因为跪禀如前所陈。则侍郎曰知道。会议上本至今未下。前见各衙门诸老爷本中。皆有敕谕等语。你等虽不说称。满朝大
闻。可得讨示耶。尚书曰会议之本。已为上进。今犹未下。当有 皇帝处置。大槩诸老爷本中有敕谕等语。你们与 国王安心。臣等又告曰老爷所言。只二三陪臣得闻。今若以此只行回咨。则不过 国王与该管陪臣知之。若明降敕书则一国远近大小臣民。皆得快睹。伏望老爷善为禀覆赐敕。使小邦君臣上下八道府州县。释然皆知昭雪冤痛之意。尚书曰阁下前亦以此意呈文耶。答曰小的等见朝日。适遇沈阁老。已为呈文矣。尚书曰知道。我当与阁下议之。你等亦何不上本于通政司乎。答曰前来陪臣李元翼为此冤痛事情。上本于通政司。本司以无 国王印信不受。小的等今虽欲上本。本司亦必不受矣。尚书又曰你等今日见王侍郎否。答曰未见。尚书即分付长班曰你可将带诸国纪五礼仪二册及陪臣等。往见于侍郎。臣等因言小的等缘情理痛迫。不觉言语猥烦。致老爷久立。不胜未安。敢叩头以谢。叩讫。因行两揖辞退。与堂所送长班。齐到右侍郎王世杨火房。侍郎亦曰陪臣等免拜。即行两揖讫。因为跪禀如前所陈。则侍郎曰知道。会议上本至今未下。前见各衙门诸老爷本中。皆有敕谕等语。你等虽不说称。满朝大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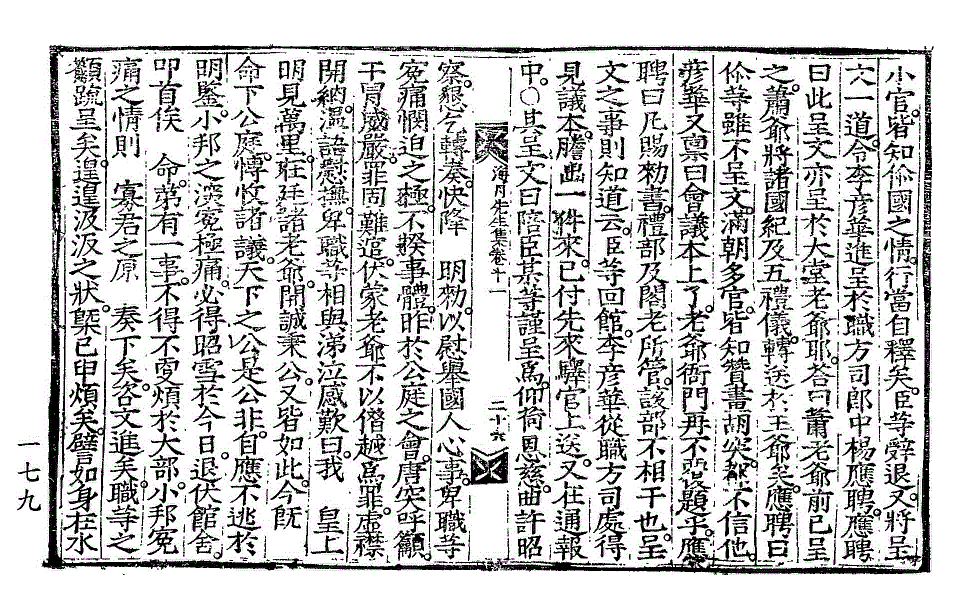 小官。皆知你国之情。行当自释矣。臣等辞退。又将呈文一道。令李彦华进呈于职方司郎中杨应聘。应聘曰此呈文亦呈于大堂老爷耶。答曰萧老爷前已呈之。萧爷将诸国纪及五礼仪。转送于王爷矣。应聘曰你等虽不呈文。满朝多官。皆知赞画胡突。都不信他。彦华又禀曰会议本上了。老爷衙门再不覆题乎。应聘曰凡赐敕书。礼部及阁老所管。该部不相干也。呈文之事则知道云。臣等回馆。李彦华从职方司处得见议本。誊出一件来。已付先来驿官上送。又在通报中。○其呈文曰陪臣某等谨呈为。仰荷恩慈。曲许昭察。恳乞转奏。快降 明敕。以慰举国人心事。卑职等冤痛悯迫之极。不揆事体。昨于公庭之会。唐突呼吁。干冒威严。罪固难逭。伏蒙老爷不以僭越为罪。虚襟开纳。温语慰抚。卑职等相与涕泣感叹曰。我 皇上明见万里。在廷诸老爷。开诚秉公。又皆如此。今既 命下公庭。博收诸议。天下之公是公非。自应不逃于明鉴。小邦之深冤极痛。必得昭雪于今日。退伏馆舍。叩首俟 命。第有一事。不得不更烦于大部。小邦冤痛之情则 寡君之原 奏下矣。咨文进矣。职等之吁疏呈矣。遑遑汲汲之状。概已申烦矣。譬如身在水
小官。皆知你国之情。行当自释矣。臣等辞退。又将呈文一道。令李彦华进呈于职方司郎中杨应聘。应聘曰此呈文亦呈于大堂老爷耶。答曰萧老爷前已呈之。萧爷将诸国纪及五礼仪。转送于王爷矣。应聘曰你等虽不呈文。满朝多官。皆知赞画胡突。都不信他。彦华又禀曰会议本上了。老爷衙门再不覆题乎。应聘曰凡赐敕书。礼部及阁老所管。该部不相干也。呈文之事则知道云。臣等回馆。李彦华从职方司处得见议本。誊出一件来。已付先来驿官上送。又在通报中。○其呈文曰陪臣某等谨呈为。仰荷恩慈。曲许昭察。恳乞转奏。快降 明敕。以慰举国人心事。卑职等冤痛悯迫之极。不揆事体。昨于公庭之会。唐突呼吁。干冒威严。罪固难逭。伏蒙老爷不以僭越为罪。虚襟开纳。温语慰抚。卑职等相与涕泣感叹曰。我 皇上明见万里。在廷诸老爷。开诚秉公。又皆如此。今既 命下公庭。博收诸议。天下之公是公非。自应不逃于明鉴。小邦之深冤极痛。必得昭雪于今日。退伏馆舍。叩首俟 命。第有一事。不得不更烦于大部。小邦冤痛之情则 寡君之原 奏下矣。咨文进矣。职等之吁疏呈矣。遑遑汲汲之状。概已申烦矣。譬如身在水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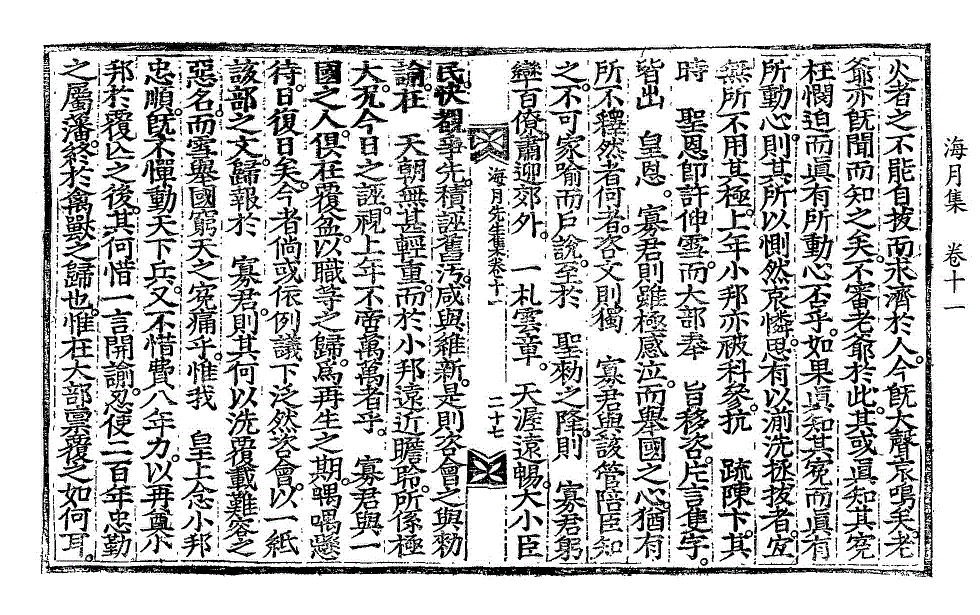 火者。之不能自拔而求济于人。今既大声哀鸣矣。老爷亦既闻而知之矣。不审老爷于此。其或真知其冤枉悯迫而真有所动心否乎。如果真知其冤而真有所动心。则其所以恻然哀怜。思有以湔洗拯拔者。宜无所不用其极。上年小邦亦被科参。抗 疏陈卞。其时 圣恩即许伸雪。而大部奉 旨移咨。片言只字。皆出 皇恩。 寡君则虽极感泣。而举国之心。犹有所不释然者何者。咨文则独 寡君与该管陪臣知之。不可家喻而户说。至于 圣敕之降。则 寡君躬率百僚。肃迎郊外。 一札云章。 天渥远畅。大小臣民。快睹争先。积诬旧污。咸与维新。是则咨会之与敕谕。在 天朝无甚轻重。而于小邦远近瞻聆。所系极大。况今日之诬。视上年不啻万万者乎。 寡君与一国之人。俱在覆盆。以职等之归。为再生之期。喁喁悬待。日复日矣。今者。倘或依例议下泛然咨会。以一纸该部之文。归报于 寡君。则其何以洗覆载难容之恶名。而雪举国穷天之冤痛乎。惟我 皇上念小邦忠顺。既不惮动天下兵。又不惜费八年力。以再奠小邦于覆亡之后。其何惜一言开谕。忍使二百年忠勤之属藩。终于禽兽之归也。惟在大部禀覆之如何耳。
火者。之不能自拔而求济于人。今既大声哀鸣矣。老爷亦既闻而知之矣。不审老爷于此。其或真知其冤枉悯迫而真有所动心否乎。如果真知其冤而真有所动心。则其所以恻然哀怜。思有以湔洗拯拔者。宜无所不用其极。上年小邦亦被科参。抗 疏陈卞。其时 圣恩即许伸雪。而大部奉 旨移咨。片言只字。皆出 皇恩。 寡君则虽极感泣。而举国之心。犹有所不释然者何者。咨文则独 寡君与该管陪臣知之。不可家喻而户说。至于 圣敕之降。则 寡君躬率百僚。肃迎郊外。 一札云章。 天渥远畅。大小臣民。快睹争先。积诬旧污。咸与维新。是则咨会之与敕谕。在 天朝无甚轻重。而于小邦远近瞻聆。所系极大。况今日之诬。视上年不啻万万者乎。 寡君与一国之人。俱在覆盆。以职等之归。为再生之期。喁喁悬待。日复日矣。今者。倘或依例议下泛然咨会。以一纸该部之文。归报于 寡君。则其何以洗覆载难容之恶名。而雪举国穷天之冤痛乎。惟我 皇上念小邦忠顺。既不惮动天下兵。又不惜费八年力。以再奠小邦于覆亡之后。其何惜一言开谕。忍使二百年忠勤之属藩。终于禽兽之归也。惟在大部禀覆之如何耳。海月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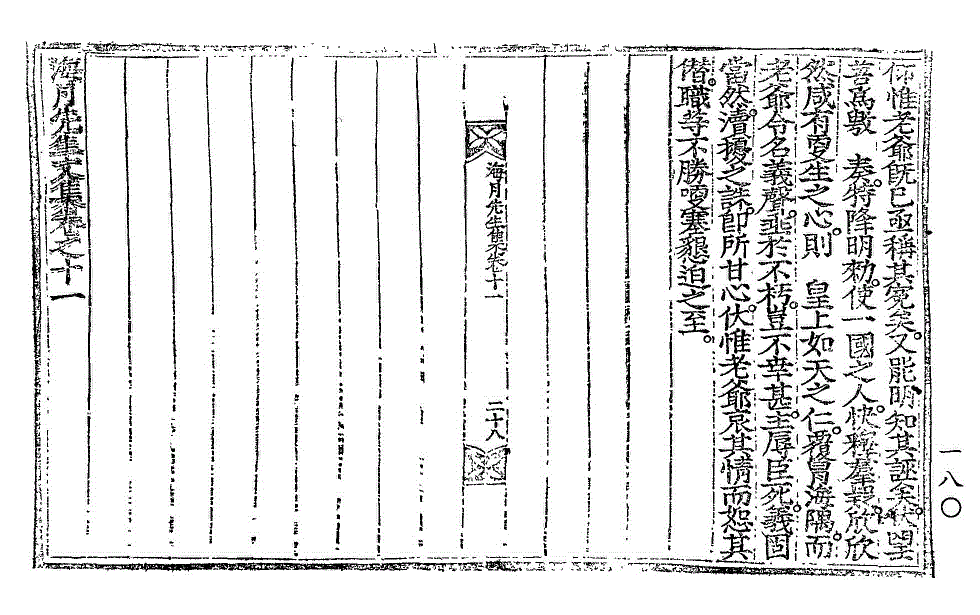 仰惟老爷既已亟称其冤矣。又能明知其诬矣。伏望善为敷 奏。特降明敕。使一国之人。快释群疑。欣欣然咸有更生之心。则 皇上如天之仁。覆冒海隅。而老爷令名义声。垂于不朽。岂不幸甚。主辱臣死。义固当然。渎扰之诛。即所甘心。伏惟老爷哀其情而恕其僭。职等不胜哽塞恳迫之至。
仰惟老爷既已亟称其冤矣。又能明知其诬矣。伏望善为敷 奏。特降明敕。使一国之人。快释群疑。欣欣然咸有更生之心。则 皇上如天之仁。覆冒海隅。而老爷令名义声。垂于不朽。岂不幸甚。主辱臣死。义固当然。渎扰之诛。即所甘心。伏惟老爷哀其情而恕其僭。职等不胜哽塞恳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