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疏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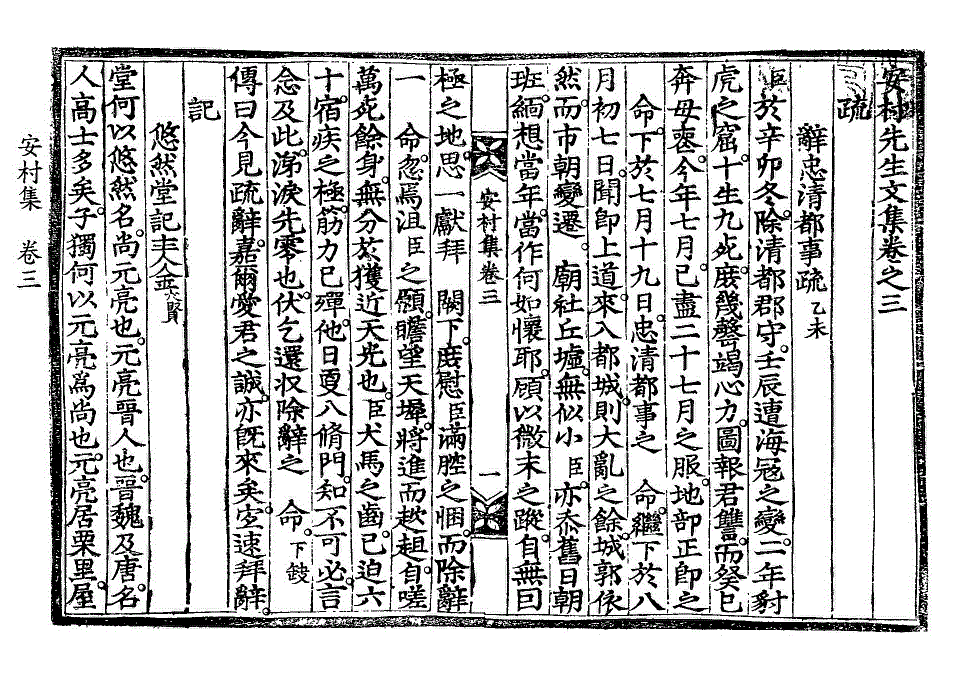 辞忠清都事疏(乙未)
辞忠清都事疏(乙未)臣于辛卯冬除清都郡守。壬辰遭海寇之变。二年豺虎之窟。十生九死。庶几罄竭心力。图报君雠。而癸巳奔母丧。今年七月。已尽二十七月之服。地部正郎之 命。下于七月十九日。忠清都事之 命。继下于八月初七日。闻即上道。来入都城。则大乱之馀。城郭依然。而市朝变迁。 庙社丘墟。无似小臣。亦忝旧日朝班。缅想当年。当作何如怀耶。顾以微末之踪。自无因极之地。思一献拜 阙下。庶慰臣满腔之悃。而除辞一 命。忽焉沮臣之愿。瞻望天墀。将进而趑趄。自嗟万死馀身。无分于获近天光也。臣犬马之齿。已迫六十。宿疾之极。筋力已殚。他日更入脩门。知不可必。言念及此。涕泪先零也。伏乞还收除辞之 命。(下缺)
传曰今见疏辞。嘉尔爱君之诚。亦既来矣。宜速拜辞。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记
悠然堂记主人金(大贤)
堂何以悠然名。尚元亮也。元亮晋人也。晋魏及唐。名人高士多矣。子独何以元亮为尚也。元亮居栗里。屋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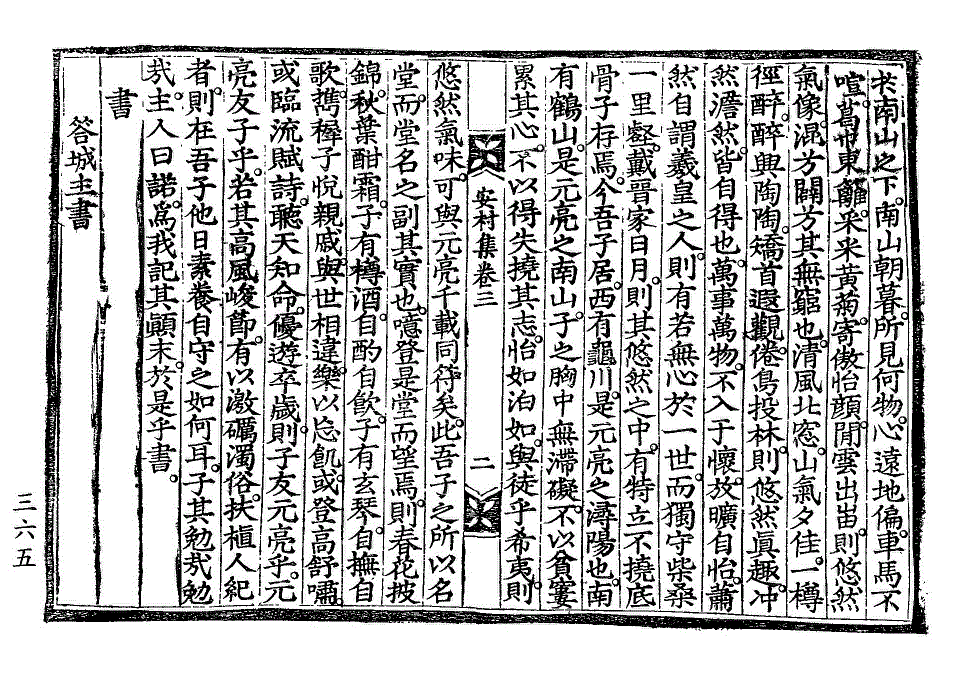 于南山之下。南山朝暮。所见何物。心远地偏。车马不喧。葛巾东篱。采采黄菊。寄傲怡颜。閒云出岫。则悠然气像。混兮辟兮其无穷也。清风北窗。山气夕佳。一樽径醉。醉兴陶陶。矫首遐观。倦鸟投林。则悠然真趣。冲然澹然。皆自得也。万事万物。不入于怀。放旷自怡。萧然自谓羲皇之人。则有若无心于一世。而独守柴桑一里壑。戴晋家日月。则其悠然之中。有特立不挠底骨子存焉。今吾子居。西有龟川。是元亮之浔阳也。南有鹤山。是元亮之南山。子之胸中无滞碍。不以贫窭累其心。不以得失挠其志。怡如泊如。与徒乎希夷。则悠然气味。可与元亮千载同符矣。此吾子之所以名堂。而堂名之副其实也。噫登是堂而望焉。则春花披锦。秋叶酣霜。子有樽酒。自酌自饮。子有玄琴。自抚自歌。携稚子悦亲戚。与世相违。乐以忘饥。或登高舒啸。或临流赋诗。听天知命。优游卒岁。则子友元亮乎。元亮友子乎。若其高风峻节。有以激砺浊俗。扶植人纪者。则在吾子他日素养自守之如何耳。子其勉哉勉哉。主人曰诺。为我记其颠末。于是乎书。
于南山之下。南山朝暮。所见何物。心远地偏。车马不喧。葛巾东篱。采采黄菊。寄傲怡颜。閒云出岫。则悠然气像。混兮辟兮其无穷也。清风北窗。山气夕佳。一樽径醉。醉兴陶陶。矫首遐观。倦鸟投林。则悠然真趣。冲然澹然。皆自得也。万事万物。不入于怀。放旷自怡。萧然自谓羲皇之人。则有若无心于一世。而独守柴桑一里壑。戴晋家日月。则其悠然之中。有特立不挠底骨子存焉。今吾子居。西有龟川。是元亮之浔阳也。南有鹤山。是元亮之南山。子之胸中无滞碍。不以贫窭累其心。不以得失挠其志。怡如泊如。与徒乎希夷。则悠然气味。可与元亮千载同符矣。此吾子之所以名堂。而堂名之副其实也。噫登是堂而望焉。则春花披锦。秋叶酣霜。子有樽酒。自酌自饮。子有玄琴。自抚自歌。携稚子悦亲戚。与世相违。乐以忘饥。或登高舒啸。或临流赋诗。听天知命。优游卒岁。则子友元亮乎。元亮友子乎。若其高风峻节。有以激砺浊俗。扶植人纪者。则在吾子他日素养自守之如何耳。子其勉哉勉哉。主人曰诺。为我记其颠末。于是乎书。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答城主书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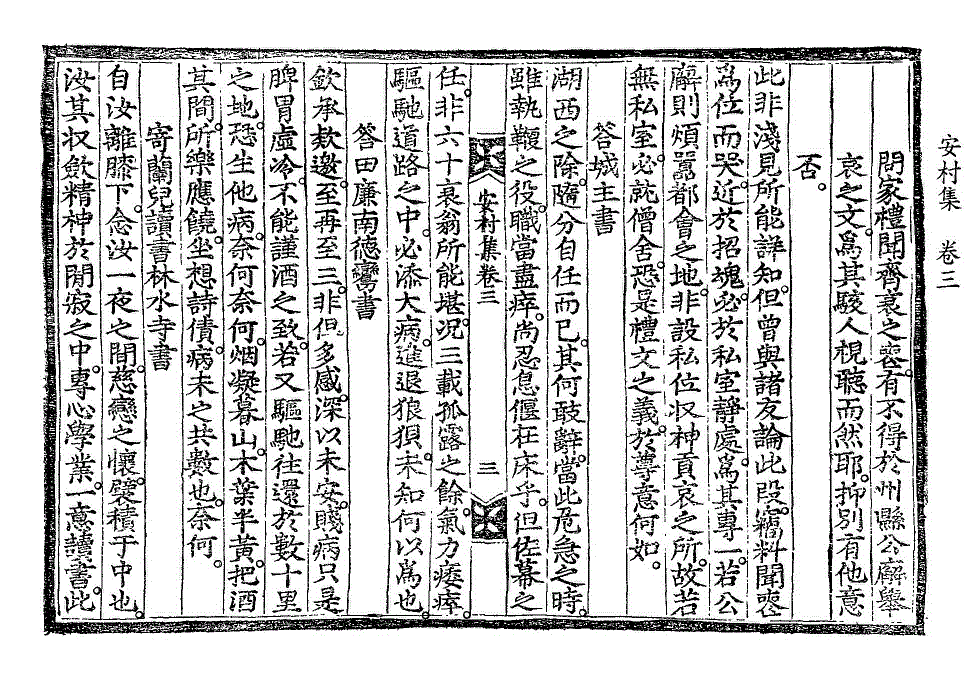 问家礼闻齐衰之丧。有不得于州县公廨举哀之文。为其骇人视听而然耶。抑别有他意否。
问家礼闻齐衰之丧。有不得于州县公廨举哀之文。为其骇人视听而然耶。抑别有他意否。此非浅见所能详知。但曾与诸友论此段。窃料闻丧为位而哭。近于招魂。必于私室静处。为其专一。若公廨则烦嚣都会之地。非设私位收神贡哀之所。故若无私室。必就僧舍。恐是礼文之义。于尊意何如。
答城主书
湖西之除。随分自任而已。其何敢辞。当此危急之时。虽执鞭之役。职当尽瘁。尚忍息偃在床乎。但佐幕之任。非六十衰翁所能堪。况三载孤露之馀。气力痿瘁。驱驰道路之中。必添大病。进退狼狈。未知何以为也。
答田廉南德鸾书
钦承款邀。至再至三。非但多感。深以未安。贱病只是脾胃虚冷。不能谨酒之致。若又驱驰往还于数十里之地。恐生他病。奈何奈何。烟凝暮山。木叶半黄。把酒其间。所乐应饶。坐想诗债。病未之共数也。奈何。
寄兰儿读书林水寺书
自汝离膝下。念汝一夜之间。慈恋之怀。襞积于中也。汝其收敛精神于閒寂之中。专心学业。一意读书。此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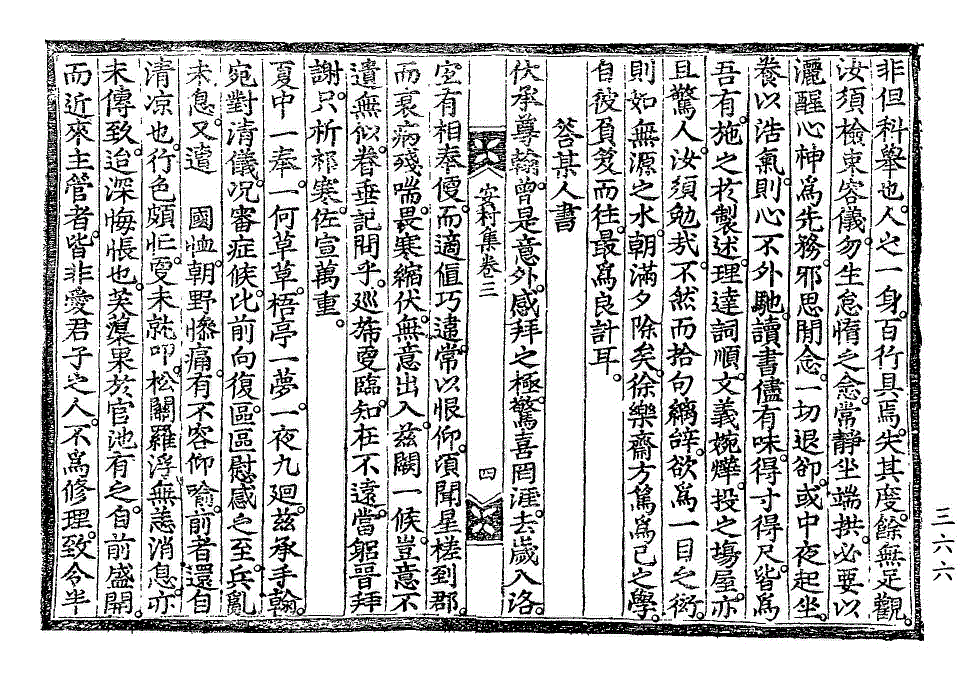 非但科举也。人之一身。百行具焉。失其度。馀无足观。汝须检束容仪。勿生怠惰之念。常静坐端拱。必要以洒醒心神为先务。邪思閒念。一切退却。或中夜起坐。养以浩气。则心不外驰。读书尽有味。得寸得尺。皆为吾有。施之于制述。理达词顺。文义婉烨。投之场屋。亦且惊人。汝须勉哉。不然而拾句缡辞。欲为一目之衒。则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矣。徐乐斋方笃为己之学。自彼负笈而往。最为良计耳。
非但科举也。人之一身。百行具焉。失其度。馀无足观。汝须检束容仪。勿生怠惰之念。常静坐端拱。必要以洒醒心神为先务。邪思閒念。一切退却。或中夜起坐。养以浩气。则心不外驰。读书尽有味。得寸得尺。皆为吾有。施之于制述。理达词顺。文义婉烨。投之场屋。亦且惊人。汝须勉哉。不然而拾句缡辞。欲为一目之衒。则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矣。徐乐斋方笃为己之学。自彼负笈而往。最为良计耳。答某人书
伏承尊翰。曾是意外。感拜之极。惊喜罔涯。去岁入洛。宜有相奉便。而适值巧违。常以恨仰。顷闻星槎到郡。而衰病残喘。畏寒缩伏。无意出入。玆阙一候。岂意不遗无似。眷垂记问乎。巡旆更临。知在不远。当躬晋拜谢。只祈祁寒。佐宣万重。
夏中一奉。一何草草。梧亭一梦。一夜九回。玆承手翰。宛对清仪。况审症候。比前向复。区区慰感之至。兵乱未息。又遭 国恤。朝野惨痛。有不容仰喻。前者还自清凉也。行色颇忙。更未就叩。松关罗浮无恙消息。亦未传致。迨深悔怅也。芙蕖果于官池有之。自前盛开。而近来主管者。皆非爱君子之人。不为修理。致令半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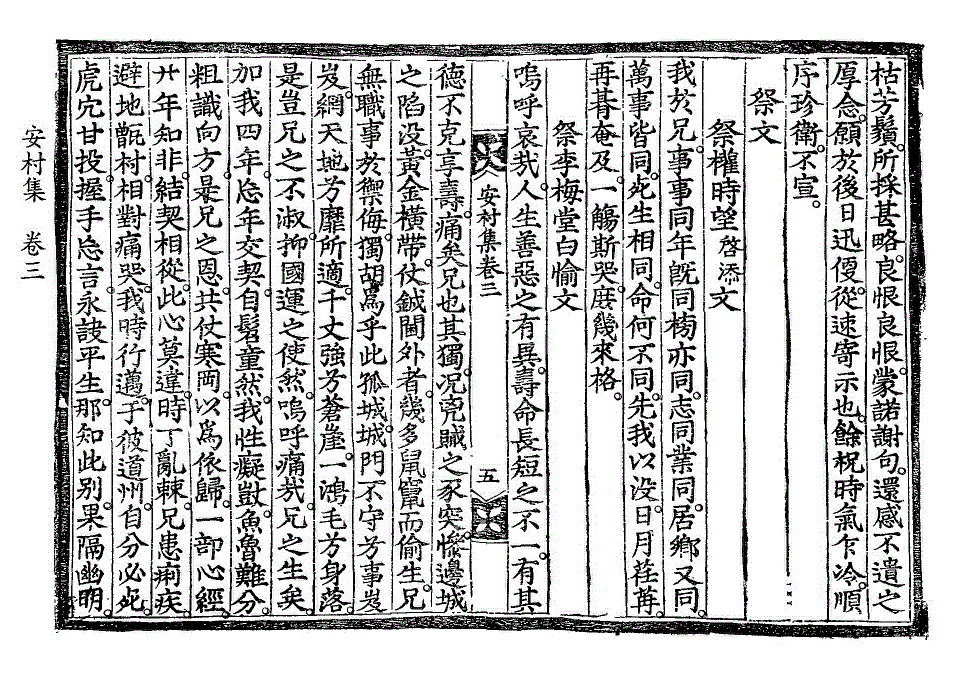 枯芳须。所采甚略。良恨良恨。蒙诺谢句。还感不遗之厚念。愿于后日迅便。从速寄示也。馀祝时气乍冷。顺序珍卫。不宣。
枯芳须。所采甚略。良恨良恨。蒙诺谢句。还感不遗之厚念。愿于后日迅便。从速寄示也。馀祝时气乍冷。顺序珍卫。不宣。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祭文
祭权时望(启添)文
我于兄。事事同年既同榜亦同。志同业同。居乡又同。万事皆同。死生相同。命何不同。先我以没。日月荏苒。再期奄及。一觞斯哭。庶几来格。
祭李梅堂白愉文
呜呼哀哉。人生善恶之有异。寿命长短之不一。有其德不克享寿。痛矣兄也其独。况凶贼之豕突。惨边城之陷没。黄金横带。仗銊阃外者。几多鼠窜而偷生。兄无职事于御侮。独胡为乎此孤城。城门不守兮事岌岌。网天地兮靡所适。千丈强兮苍崖。一鸿毛兮身落。是岂兄之不淑。抑国运之使然。呜呼痛哉。兄之生矣。加我四年。忘年交契。自髫童然。我性痴呆。鱼鲁难分。粗识向方。是兄之恩。共仗寒冈。以为依归。一部心经。廿年知非。结契相从。此心莫违。时丁乱棘。兄患痢疾。避地甑村。相对痛哭。我时行迈。于彼道州。自分必死。虎穴甘投。握手忘言。永诀平生。那知此别。果隔幽明。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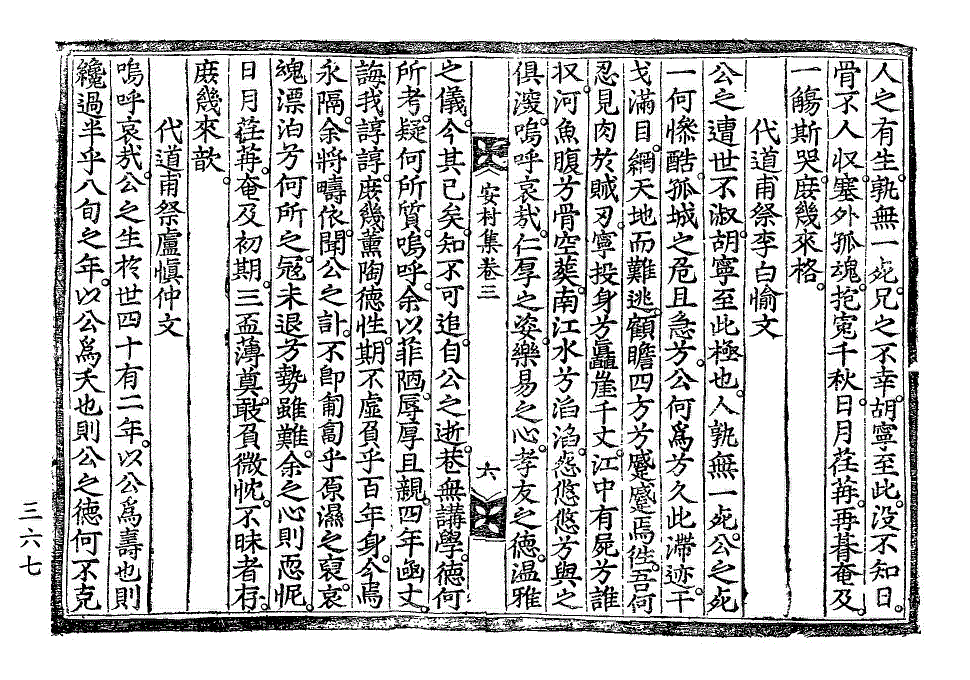 人之有生。孰无一死。兄之不幸。胡宁至此。没不知日。骨不人收。塞外孤魂。抱冤千秋。日月荏苒。再期奄及。一觞斯哭。庶几来格。
人之有生。孰无一死。兄之不幸。胡宁至此。没不知日。骨不人收。塞外孤魂。抱冤千秋。日月荏苒。再期奄及。一觞斯哭。庶几来格。代道甫祭李白愉文
公之遭世不淑。胡宁至此极也。人孰无一死。公之死一何惨酷。孤城之危且急兮。公何为兮久此滞迹。干戈满目。网天地而难逃。顾瞻四方兮蹙蹙焉往。吾何忍见肉于贼刃。宁投身兮矗崖千丈。江中有尸兮谁收。河鱼腹兮骨空葬。南江水兮淊淊。怨悠悠兮与之俱深。呜呼哀哉。仁厚之姿。乐易之心。孝友之德。温雅之仪。今其已矣。知不可追。自公之逝。巷无讲学。德何所考。疑何所质。呜呼。余以菲陋。辱厚且亲。四年函丈。诲我谆谆。庶几薰陶德性。期不虚负乎百年身。今焉永隔。余将畴依。闻公之讣。不即匍匐乎原湿之裒。哀魂漂泊兮何所之。寇未退兮势虽难。余之心则恧怩。日月荏苒。奄及初期。三杯薄奠。敢负微忱。不昧者存。庶几来歆。
代道甫祭卢慎仲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四十有二年。以公为寿也则才过半乎八旬之年。以公为夭也则公之德何不克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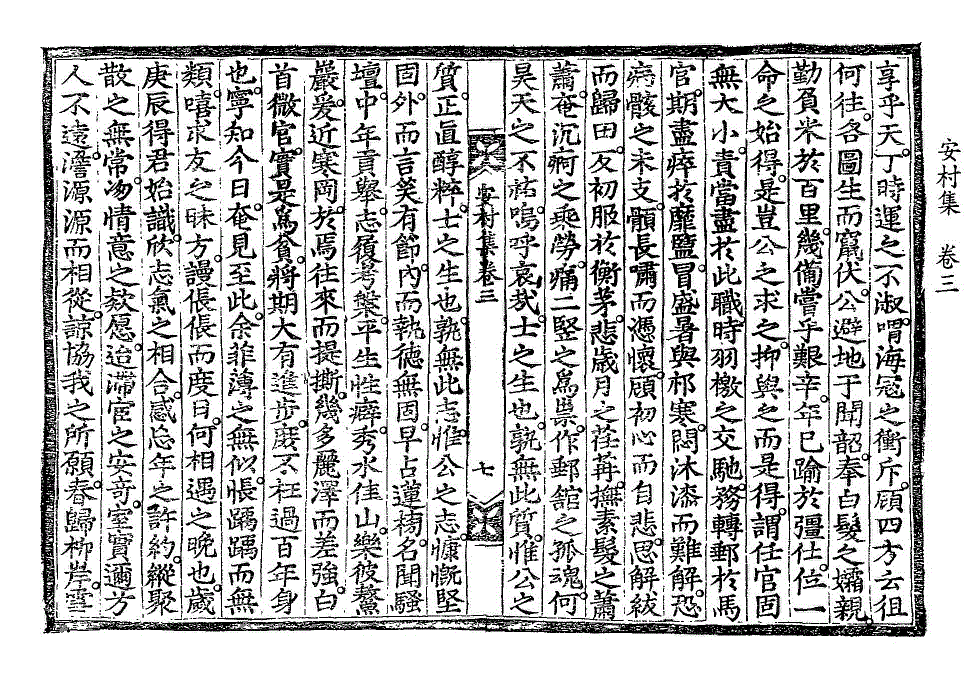 享乎天。丁时运之不淑。喟海寇之冲斥。顾四方云徂何往。各图生而窜伏。公避地于闻韶。奉白发之孀亲。勤负米于百里。几备尝乎艰辛。年已踰于彊仕。位一命之始得。是岂公之求之。抑与之而是得。谓任官固无大小。责当尽于此职。时羽檄之交驰。务转邮于马官。期尽瘁于靡盬。冒盛暑与祁寒。闷沐漆而难解。恐病骸之未支。顝长啸而凭怀。顾初心而自悲。思解绂而归田。反初服于衡茅。悲岁月之荏苒。抚素发之萧萧。奄沈痾之乘劳。痛二竖之为祟。作邮馆之孤魂。何昊天之不祐。呜呼哀哉。士之生也。孰无此质。惟公之质。正直醇粹。士之生也。孰无此志。惟公之志。慷慨坚固。外而言笑有节。内而执德无固。早占莲榜。名闻骚坛。中年贡举。志履考槃。平生性癖。秀水佳山。乐彼鳌岩。爰近寒冈。于焉往来而提撕。几多丽泽而差强。白首微官。实是为贫。将期大有进步。庶不枉过百年身也。宁知今日。奄见至此。余菲薄之无似。怅踽踽而无类。嘻求友之昧方。谩伥伥而度日。何相遇之晚也。岁庚辰得君始识。欣志气之相合。感忘年之许约。纵聚散之无常。沕情意之款愿。迨滞宦之安奇。室实迩兮人不远。澹源源而相从。谅协我之所愿。春归柳岸。雪
享乎天。丁时运之不淑。喟海寇之冲斥。顾四方云徂何往。各图生而窜伏。公避地于闻韶。奉白发之孀亲。勤负米于百里。几备尝乎艰辛。年已踰于彊仕。位一命之始得。是岂公之求之。抑与之而是得。谓任官固无大小。责当尽于此职。时羽檄之交驰。务转邮于马官。期尽瘁于靡盬。冒盛暑与祁寒。闷沐漆而难解。恐病骸之未支。顝长啸而凭怀。顾初心而自悲。思解绂而归田。反初服于衡茅。悲岁月之荏苒。抚素发之萧萧。奄沈痾之乘劳。痛二竖之为祟。作邮馆之孤魂。何昊天之不祐。呜呼哀哉。士之生也。孰无此质。惟公之质。正直醇粹。士之生也。孰无此志。惟公之志。慷慨坚固。外而言笑有节。内而执德无固。早占莲榜。名闻骚坛。中年贡举。志履考槃。平生性癖。秀水佳山。乐彼鳌岩。爰近寒冈。于焉往来而提撕。几多丽泽而差强。白首微官。实是为贫。将期大有进步。庶不枉过百年身也。宁知今日。奄见至此。余菲薄之无似。怅踽踽而无类。嘻求友之昧方。谩伥伥而度日。何相遇之晚也。岁庚辰得君始识。欣志气之相合。感忘年之许约。纵聚散之无常。沕情意之款愿。迨滞宦之安奇。室实迩兮人不远。澹源源而相从。谅协我之所愿。春归柳岸。雪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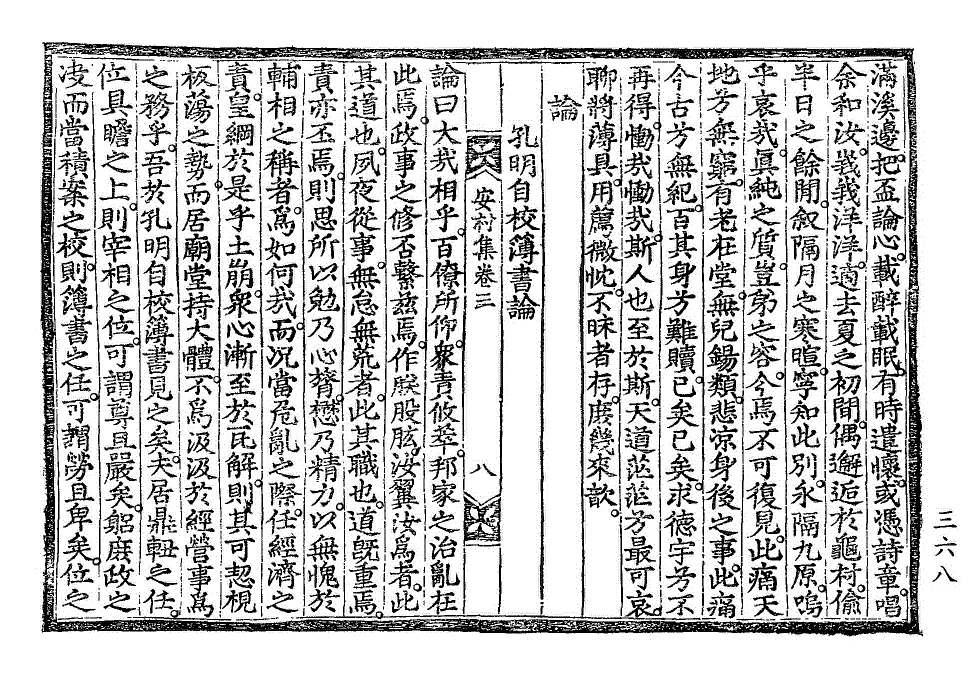 满溪边。把杯论心。载醉载眠。有时遣怀。或凭诗章。唱余和汝。峨峨洋洋。适去夏之初间。偶邂逅于龟村。偷半日之馀閒。叙隔月之寒暄。宁知此别。永隔九原。呜乎哀哉。真纯之质。岂弟之容。今焉不可复见。此痛天地兮无穷。有老在堂。无儿锡类。悲凉身后之事。此痛今古兮无纪。百其身兮难赎。已矣已矣。求德宇兮不再得。恸哉恸哉。斯人也至于斯。天道茫茫兮最可哀。聊将薄具。用荐微忱。不昧者存。庶几来歆。
满溪边。把杯论心。载醉载眠。有时遣怀。或凭诗章。唱余和汝。峨峨洋洋。适去夏之初间。偶邂逅于龟村。偷半日之馀閒。叙隔月之寒暄。宁知此别。永隔九原。呜乎哀哉。真纯之质。岂弟之容。今焉不可复见。此痛天地兮无穷。有老在堂。无儿锡类。悲凉身后之事。此痛今古兮无纪。百其身兮难赎。已矣已矣。求德宇兮不再得。恸哉恸哉。斯人也至于斯。天道茫茫兮最可哀。聊将薄具。用荐微忱。不昧者存。庶几来歆。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论
孔明自校簿书论
论曰大哉相乎。百僚所仰。众责攸萃。邦家之治乱在此焉。政事之修否系玆焉。作朕股肱。汝翼汝为者。此其道也。夙夜从事。无怠无荒者。此其职也。道既重焉。责亦丕焉。则思所以勉乃心膂。懋乃精力。以无愧于辅相之称者。为如何哉。而况当危乱之际。任经济之责。皇纲于是乎土崩。众心渐至于瓦解。则其可恝视板荡之势。而居庙堂持大体。不为汲汲于经营事为之务乎。吾于孔明自校簿书见之矣。夫居鼎轴之任。位具瞻之上。则宰相之位。可谓尊且严矣。躬庶政之决而当积案之校。则簿书之任。可谓劳且卑矣。位之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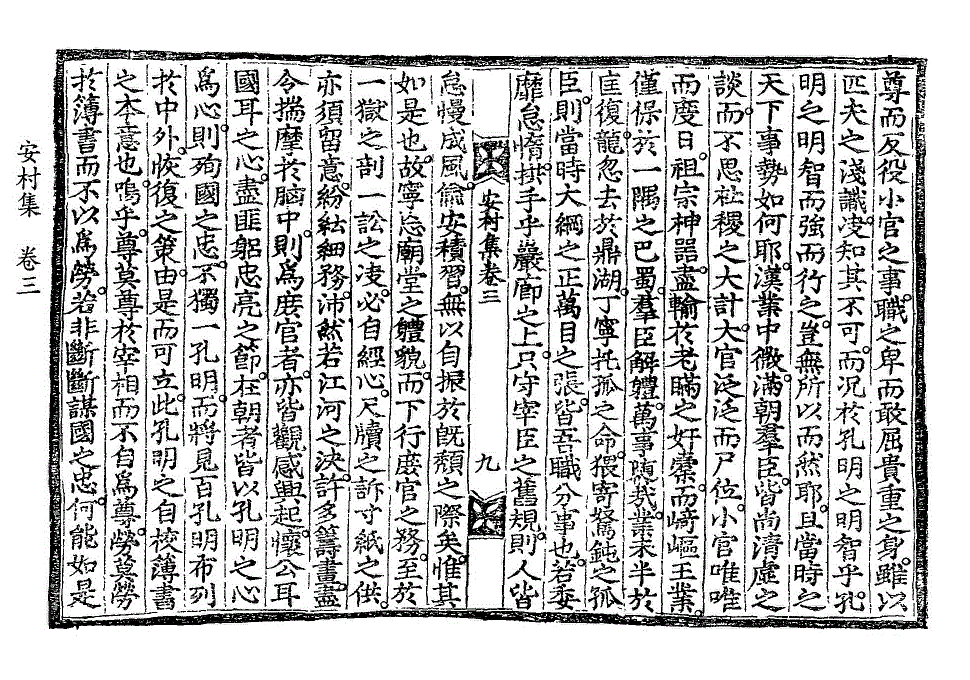 尊而反役小官之事。职之卑而敢屈贵重之身。虽以匹夫之浅识。决知其不可。而况于孔明之明智乎。孔明之明智而强而行之。岂无所以而然耶。且当时之天下事势如何耶。汉业中微。满朝群臣。皆尚清虚之谈。而不思社稷之大计。大官泛泛而尸位。小官唯唯而度日。祖宗神器。尽输于老瞒之奸橐。而崎岖王业。仅保于一隅之巴蜀。群臣解体。万事隳哉。业未半于匡复。龙忽去于鼎湖。丁宁托孤之命。猥寄驽钝之孤臣。则当时大纲之正万目之张。皆吾职分事也。若委靡怠惰。拱手乎岩廊之上。只守宰臣之旧规。则人皆怠慢成风。偷安积习。无以自振于既颓之际矣。惟其如是也。故宁忘庙堂之体貌。而下行庶官之务。至于一狱之剖一讼之决。必自经心。尺牍之诉寸纸之供。亦须留意。纷纭细务。沛然若江河之决。许多筹画。尽令揣摩于胸中。则为庶官者。亦皆观感兴起。怀公耳国耳之心。尽匪躬忠亮之节。在朝者皆以孔明之心为心。则殉国之忠。不独一孔明。而将见百孔明布列于中外。恢复之策。由是而可立。此孔明之自校簿书之本意也。呜乎。尊莫尊于宰相而不自为尊。劳莫劳于簿书而不以为劳。若非断断谋国之忠。何能如是
尊而反役小官之事。职之卑而敢屈贵重之身。虽以匹夫之浅识。决知其不可。而况于孔明之明智乎。孔明之明智而强而行之。岂无所以而然耶。且当时之天下事势如何耶。汉业中微。满朝群臣。皆尚清虚之谈。而不思社稷之大计。大官泛泛而尸位。小官唯唯而度日。祖宗神器。尽输于老瞒之奸橐。而崎岖王业。仅保于一隅之巴蜀。群臣解体。万事隳哉。业未半于匡复。龙忽去于鼎湖。丁宁托孤之命。猥寄驽钝之孤臣。则当时大纲之正万目之张。皆吾职分事也。若委靡怠惰。拱手乎岩廊之上。只守宰臣之旧规。则人皆怠慢成风。偷安积习。无以自振于既颓之际矣。惟其如是也。故宁忘庙堂之体貌。而下行庶官之务。至于一狱之剖一讼之决。必自经心。尺牍之诉寸纸之供。亦须留意。纷纭细务。沛然若江河之决。许多筹画。尽令揣摩于胸中。则为庶官者。亦皆观感兴起。怀公耳国耳之心。尽匪躬忠亮之节。在朝者皆以孔明之心为心。则殉国之忠。不独一孔明。而将见百孔明布列于中外。恢复之策。由是而可立。此孔明之自校簿书之本意也。呜乎。尊莫尊于宰相而不自为尊。劳莫劳于簿书而不以为劳。若非断断谋国之忠。何能如是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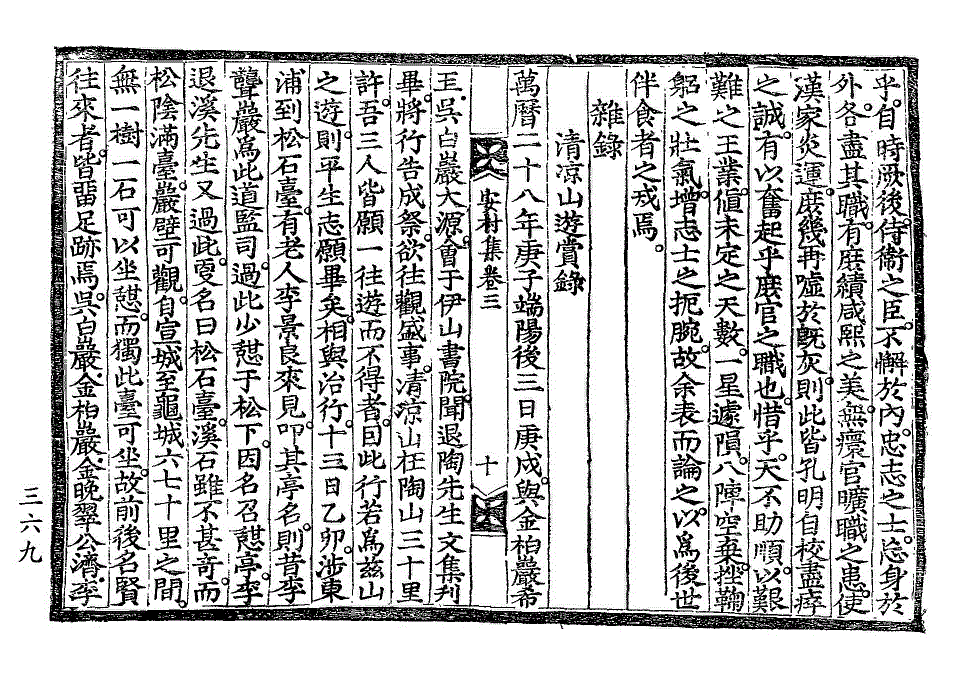 乎。自时厥后。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各尽其职。有庶绩咸熙之美。无瘝官旷职之患。使汉家炎运。庶几再嘘于既灰。则此皆孔明自校尽瘁之诚。有以奋起乎庶官之职也。惜乎。天不助顺。以艰难之王业。值未定之天数。一星遽陨。八阵空弃。挫鞠躬之壮气。增志士之扼腕。故余表而论之。以为后世伴食者之戒焉。
乎。自时厥后。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各尽其职。有庶绩咸熙之美。无瘝官旷职之患。使汉家炎运。庶几再嘘于既灰。则此皆孔明自校尽瘁之诚。有以奋起乎庶官之职也。惜乎。天不助顺。以艰难之王业。值未定之天数。一星遽陨。八阵空弃。挫鞠躬之壮气。增志士之扼腕。故余表而论之。以为后世伴食者之戒焉。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杂录
清凉山游赏录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端阳后三日庚戌。与金柏岩希玉,吴白岩大源。会于伊山书院。闻退陶先生文集刋毕。将行告成祭。欲往观盛事。清凉山在陶山三十里许。吾三人皆愿一往游而不得者。因此行若为玆山之游。则平生志愿毕矣。相与治行。十三日乙卯。涉东浦到松石台。有老人李景良来见。叩其亭名。则昔李聋岩为此道监司。过此少憩于松下。因名召憩亭。李退溪先生又过此。更名曰松石台。溪石虽不甚奇。而松阴满台。岩壁可观。自宣城至龟城六七十里之间。无一树一石可以坐憩。而独此台可坐。故前后名贤往来者。皆留足迹焉。吴白岩,金柏岩,金晚翠公济,李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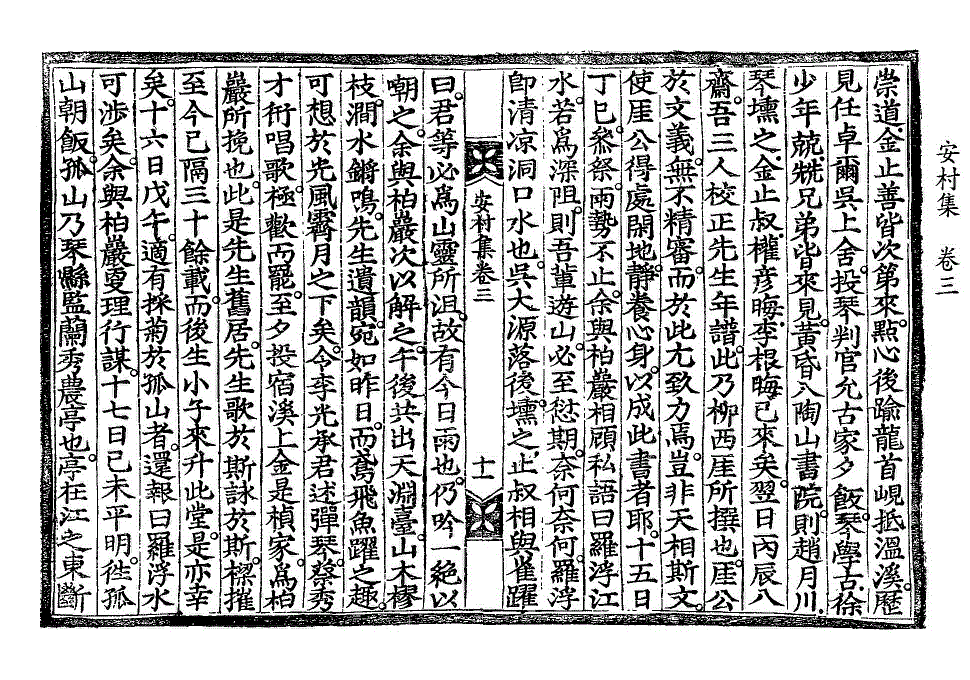 崇道,金止善皆次第来。点心后踰龙首岘抵温溪。历见任卓尔吴上舍。投琴判官允古家夕饭。琴学古,徐少年兢,兟兄弟皆来见。黄昏入陶山书院。则赵月川,琴埙之,金止叔,权彦晦,李根晦已来矣。翌日丙辰入斋。吾三人校正先生年谱。此乃柳西厓所撰也。厓公于文义。无不精审。而于此尤致力焉。岂非天相斯文。使厓公得处闲地。静养心身。以成此书者耶。十五日丁巳。参祭。雨势不止。余与柏岩相顾私语曰罗浮江水。若为深阻。则吾辈游山。必至愆期。奈何奈何。罗浮即清凉洞口水也。吴大源落后。埙之,止叔相与雀躣曰。君等必为山灵所沮。故有今日雨也。仍吟一绝以嘲之。余与柏岩次以解之。午后共出天渊台。山木樛枝。涧水锵鸣。先生遗韵。宛如昨日。而鸢飞鱼跃之趣。可想于光风霁月之下矣。令李光承君述弹琴。蔡秀才衎唱歌。极欢而罢。至夕投宿溪上金是桢家。为柏岩所挽也。此是先生旧居。先生歌于斯咏于斯。梁摧至今已隔三十馀载。而后生小子来升此堂。是亦幸矣。十六日戊午。适有采菊于孤山者。还报曰罗浮水可涉矣。余与柏岩更理行谋。十七日己未平明。往孤山朝饭。孤山乃琴县监兰秀农亭也。亭在江之东断
崇道,金止善皆次第来。点心后踰龙首岘抵温溪。历见任卓尔吴上舍。投琴判官允古家夕饭。琴学古,徐少年兢,兟兄弟皆来见。黄昏入陶山书院。则赵月川,琴埙之,金止叔,权彦晦,李根晦已来矣。翌日丙辰入斋。吾三人校正先生年谱。此乃柳西厓所撰也。厓公于文义。无不精审。而于此尤致力焉。岂非天相斯文。使厓公得处闲地。静养心身。以成此书者耶。十五日丁巳。参祭。雨势不止。余与柏岩相顾私语曰罗浮江水。若为深阻。则吾辈游山。必至愆期。奈何奈何。罗浮即清凉洞口水也。吴大源落后。埙之,止叔相与雀躣曰。君等必为山灵所沮。故有今日雨也。仍吟一绝以嘲之。余与柏岩次以解之。午后共出天渊台。山木樛枝。涧水锵鸣。先生遗韵。宛如昨日。而鸢飞鱼跃之趣。可想于光风霁月之下矣。令李光承君述弹琴。蔡秀才衎唱歌。极欢而罢。至夕投宿溪上金是桢家。为柏岩所挽也。此是先生旧居。先生歌于斯咏于斯。梁摧至今已隔三十馀载。而后生小子来升此堂。是亦幸矣。十六日戊午。适有采菊于孤山者。还报曰罗浮水可涉矣。余与柏岩更理行谋。十七日己未平明。往孤山朝饭。孤山乃琴县监兰秀农亭也。亭在江之东断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0L 页
 崖下。前后层岩。皆高百尺。到亭下为澄潭。招小舟荡漾中流。飘飘有凭虚羽化之趣。主人一宰凤城。三岁不来。亭边梅菊。总为芜秽。守者曰窗外有好品霜花十馀丛。今春移栽于凤城衙中云。壁上有退溪韵。余与柏岩和之。又吟成一绝付壁。以嘲主人。食后将涉罗浮。水深不可揭。令从者姜汉水前导。借得店牛。一行皆递骑利涉。午后入清凉洞口。山路百曲。树林阴翳。仰不见天日。洞门望见金塔峰。始觉境界果与他山迥超也。路左有垒石处。问之。曰昔化主僧。死为三角牛。常一载米十馀斛。不待牵夫。自往自来。大有功于僧家。故死后埋此地。留其皮以被法鼓之面云。此真诞语也。入莲台寺暂憩。石城周遭过半崩颓。问诸居僧。则往在癸巳年閒。前县监李庭桧嘱体察使李元翼监筑此城。为避贼计也云。噫自古地利不如人和。虽有金城。无人防守。则反为彼贼之所据。岭南六十州。山城设险。在在皆然。而丁酉之贼。拦入腹内。无一把截。则此山之役。非筑城也。乃筑怨也。日气阴黑有雨徵。即决然先登金塔峰。是峰在莲台寺之正南。峰之腰西。有般若台极爽豁。数步许有致远台。台右岩底。有水盈臼。人言饮此水则聪明必倍。崔致远尝
崖下。前后层岩。皆高百尺。到亭下为澄潭。招小舟荡漾中流。飘飘有凭虚羽化之趣。主人一宰凤城。三岁不来。亭边梅菊。总为芜秽。守者曰窗外有好品霜花十馀丛。今春移栽于凤城衙中云。壁上有退溪韵。余与柏岩和之。又吟成一绝付壁。以嘲主人。食后将涉罗浮。水深不可揭。令从者姜汉水前导。借得店牛。一行皆递骑利涉。午后入清凉洞口。山路百曲。树林阴翳。仰不见天日。洞门望见金塔峰。始觉境界果与他山迥超也。路左有垒石处。问之。曰昔化主僧。死为三角牛。常一载米十馀斛。不待牵夫。自往自来。大有功于僧家。故死后埋此地。留其皮以被法鼓之面云。此真诞语也。入莲台寺暂憩。石城周遭过半崩颓。问诸居僧。则往在癸巳年閒。前县监李庭桧嘱体察使李元翼监筑此城。为避贼计也云。噫自古地利不如人和。虽有金城。无人防守。则反为彼贼之所据。岭南六十州。山城设险。在在皆然。而丁酉之贼。拦入腹内。无一把截。则此山之役。非筑城也。乃筑怨也。日气阴黑有雨徵。即决然先登金塔峰。是峰在莲台寺之正南。峰之腰西。有般若台极爽豁。数步许有致远台。台右岩底。有水盈臼。人言饮此水则聪明必倍。崔致远尝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1H 页
 饮此水。故多聪明。入中土擅文名云。噫人之聪钝。自有其性。而亦由所养之如何。一勺之水。岂能使人变钝为聪哉。孤云明达之士。性本聪明。何取于水也。行数步有致远庵。无僧久矣。堂壁颓落。逢骤雨入憩。壁上有陶翁题名。又五六步许有克一庵。亦荒废无僧。庵之檐西有风穴台。以台而为窟。岩石天成。覆压平临。有似帐幕。其中可容十馀人。风雨不能入。东西皆通穴。孤云棋局尚在。自庵后旁穿绕缘梯登是台。真是台中别区也。数步有安中庵。安中乃女人也。尝有功于守护此山诸刹。故以名庵。庵下建半间祠。造木像以奉之。更数步有灵山殿。殿西有华严台极高豁。二步许有上清凉寺。久为荒废。有僧行正。修理入居才一月矣。千尺危岩。穹隆压临于庵东。雨雪不能侵。入居僧不设厨宇。列鼎岩根。常以为炊爨之所。岩腹石缝。有水点滴。以小槽承之。其傍有下清凉寺。无僧荒陋。东迤数十步。有擎日庵。亦无僧。路险未得往。日已夕矣。更转山腰前路。投宿下大乘庵。是夜风雨大作。十八日庚申。雨势小止。坐见苍崖绝壁飞流之大者小者脩者短者。冲风吹散。万条垂玉。极壮观也。历上大乘,文殊,普贤庵。登览中台。则眼界极宽豁。转往
饮此水。故多聪明。入中土擅文名云。噫人之聪钝。自有其性。而亦由所养之如何。一勺之水。岂能使人变钝为聪哉。孤云明达之士。性本聪明。何取于水也。行数步有致远庵。无僧久矣。堂壁颓落。逢骤雨入憩。壁上有陶翁题名。又五六步许有克一庵。亦荒废无僧。庵之檐西有风穴台。以台而为窟。岩石天成。覆压平临。有似帐幕。其中可容十馀人。风雨不能入。东西皆通穴。孤云棋局尚在。自庵后旁穿绕缘梯登是台。真是台中别区也。数步有安中庵。安中乃女人也。尝有功于守护此山诸刹。故以名庵。庵下建半间祠。造木像以奉之。更数步有灵山殿。殿西有华严台极高豁。二步许有上清凉寺。久为荒废。有僧行正。修理入居才一月矣。千尺危岩。穹隆压临于庵东。雨雪不能侵。入居僧不设厨宇。列鼎岩根。常以为炊爨之所。岩腹石缝。有水点滴。以小槽承之。其傍有下清凉寺。无僧荒陋。东迤数十步。有擎日庵。亦无僧。路险未得往。日已夕矣。更转山腰前路。投宿下大乘庵。是夜风雨大作。十八日庚申。雨势小止。坐见苍崖绝壁飞流之大者小者脩者短者。冲风吹散。万条垂玉。极壮观也。历上大乘,文殊,普贤庵。登览中台。则眼界极宽豁。转往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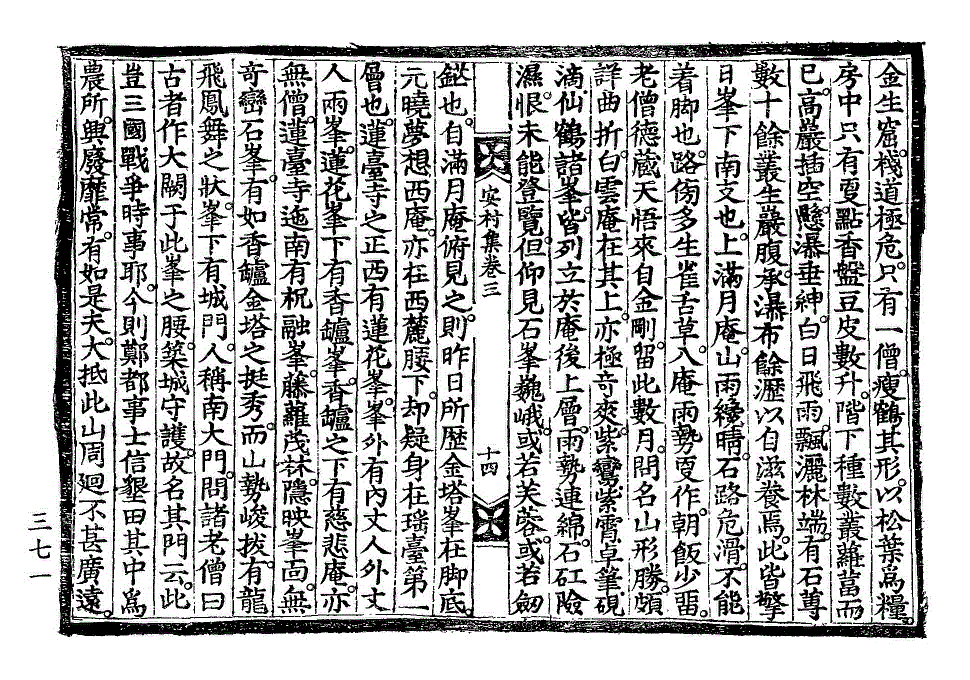 金生窟。栈道极危。只有一僧。瘦鹤其形。以松叶为粮。房中只有更点香盘豆皮数升。阶下种数丛萝葍而已。高岩插空。悬瀑垂绅。白日飞雨。飘洒林端。有石蒪数十馀丛生岩腹。承瀑布馀沥以自滋养焉。此皆擎日峰下南支也。上满月庵。山雨才晴。石路危滑。不能着脚也。路傍多生雀舌草。入庵雨势更作。朝饭少留。老僧德藏天悟来自金刚。留此数月。问名山形胜。颇详曲折。白云庵在其上。亦极奇爽。紫鸾,紫霄,卓笔,砚滴,仙鹤诸峰。皆列立于庵后上层。雨势连绵。石矼险湿。恨未能登览。但仰见石峰巍峨。或若芙蓉。或若剑铓也。自满月庵俯见之。则昨日所历金塔峰在脚底。元晓梦想西庵。亦在西麓腰下。却疑身在瑶台第一层也。莲台寺之正西有莲花峰。峰外有内丈人外丈人两峰。莲花峰下有香垆峰。香垆之下有慈悲庵。亦无僧。莲台寺迤南有祝融峰。藤萝茂林。隐映峰面。无奇峦石峰。有如香垆金塔之挺秀。而山势峻拔。有龙飞凤舞之状。峰下有城门。人称南大门。问诸老僧曰古者作大阙于此峰之腰。筑城守护。故名其门云。此岂三国战争时事耶。今则郑都事士信垦田其中为农所。兴废靡常。有如是夫。大抵此山周回不甚广远。
金生窟。栈道极危。只有一僧。瘦鹤其形。以松叶为粮。房中只有更点香盘豆皮数升。阶下种数丛萝葍而已。高岩插空。悬瀑垂绅。白日飞雨。飘洒林端。有石蒪数十馀丛生岩腹。承瀑布馀沥以自滋养焉。此皆擎日峰下南支也。上满月庵。山雨才晴。石路危滑。不能着脚也。路傍多生雀舌草。入庵雨势更作。朝饭少留。老僧德藏天悟来自金刚。留此数月。问名山形胜。颇详曲折。白云庵在其上。亦极奇爽。紫鸾,紫霄,卓笔,砚滴,仙鹤诸峰。皆列立于庵后上层。雨势连绵。石矼险湿。恨未能登览。但仰见石峰巍峨。或若芙蓉。或若剑铓也。自满月庵俯见之。则昨日所历金塔峰在脚底。元晓梦想西庵。亦在西麓腰下。却疑身在瑶台第一层也。莲台寺之正西有莲花峰。峰外有内丈人外丈人两峰。莲花峰下有香垆峰。香垆之下有慈悲庵。亦无僧。莲台寺迤南有祝融峰。藤萝茂林。隐映峰面。无奇峦石峰。有如香垆金塔之挺秀。而山势峻拔。有龙飞凤舞之状。峰下有城门。人称南大门。问诸老僧曰古者作大阙于此峰之腰。筑城守护。故名其门云。此岂三国战争时事耶。今则郑都事士信垦田其中为农所。兴废靡常。有如是夫。大抵此山周回不甚广远。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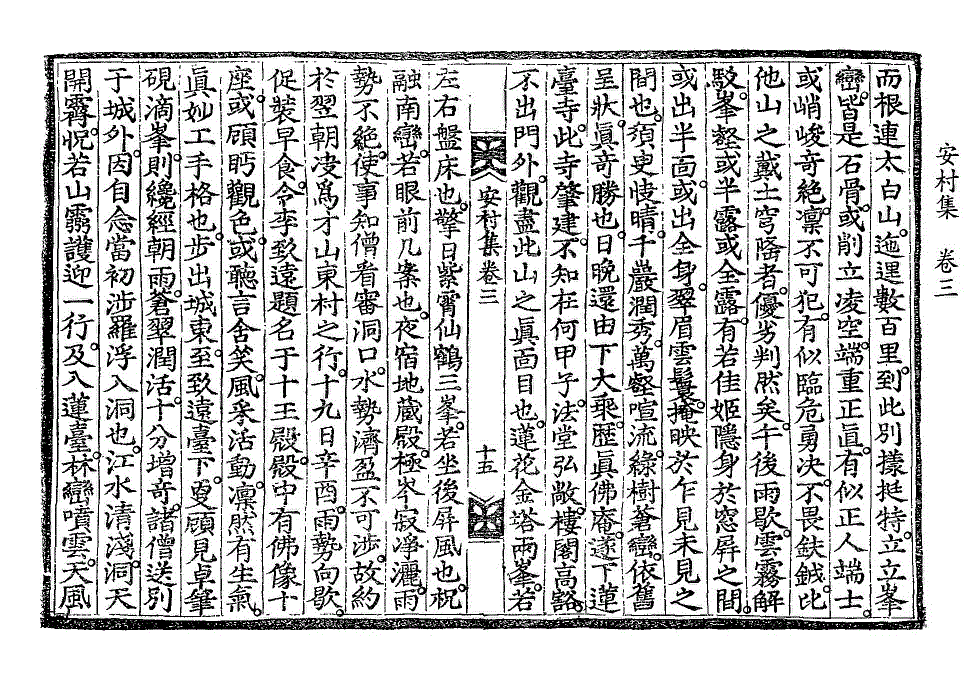 而根连太白山。迤𨓦数百里。到此别㨾挺特。立立峰峦。皆是石骨。或削立凌空。端重正直。有似正人端士。或峭峻奇绝。凛不可犯。有似临危勇决。不畏鈇銊。比他山之戴土穹隆者。优劣判然矣。午后雨歇。云雾解驳。峰壑或半露或全露。有若佳姬隐身于窗屏之间。或出半面。或出全身。翠眉云鬟。掩映于乍见未见之间也。须臾快晴。千岩润秀。万壑喧流。绿树苍峦。依旧呈状。真奇胜也。日晚还由下大乘。历真佛庵。遂下莲台寺。此寺肇建。不知在何甲子。法堂弘敞。楼阁高豁。不出门外。观尽此山之真面目也。莲花金塔两峰。若左右盘床也。擎日紫霄仙鹤三峰。若坐后屏风也。祝融南峦。若眼前几案也。夜宿地藏殿。极岑寂净洒。雨势不绝。使事知僧看审洞口。水势济盈不可涉。故约于翌朝决为才山东村之行。十九日辛酉。雨势向歇。促装早食。令李致远题名于十王殿。殿中有佛像十座。或顾眄观色。或听言含笑。风采活动。凛然有生气。真妙工手格也。步出城东。至致远台下。更顾见卓笔砚滴峰。则才经朝雨。苍翠润活。十分增奇。诸僧送别于城外。因自念当初涉罗浮入洞也。江水清浅。洞天开霁。恍若山灵护迎一行。及入莲台。林峦喷云。天风
而根连太白山。迤𨓦数百里。到此别㨾挺特。立立峰峦。皆是石骨。或削立凌空。端重正直。有似正人端士。或峭峻奇绝。凛不可犯。有似临危勇决。不畏鈇銊。比他山之戴土穹隆者。优劣判然矣。午后雨歇。云雾解驳。峰壑或半露或全露。有若佳姬隐身于窗屏之间。或出半面。或出全身。翠眉云鬟。掩映于乍见未见之间也。须臾快晴。千岩润秀。万壑喧流。绿树苍峦。依旧呈状。真奇胜也。日晚还由下大乘。历真佛庵。遂下莲台寺。此寺肇建。不知在何甲子。法堂弘敞。楼阁高豁。不出门外。观尽此山之真面目也。莲花金塔两峰。若左右盘床也。擎日紫霄仙鹤三峰。若坐后屏风也。祝融南峦。若眼前几案也。夜宿地藏殿。极岑寂净洒。雨势不绝。使事知僧看审洞口。水势济盈不可涉。故约于翌朝决为才山东村之行。十九日辛酉。雨势向歇。促装早食。令李致远题名于十王殿。殿中有佛像十座。或顾眄观色。或听言含笑。风采活动。凛然有生气。真妙工手格也。步出城东。至致远台下。更顾见卓笔砚滴峰。则才经朝雨。苍翠润活。十分增奇。诸僧送别于城外。因自念当初涉罗浮入洞也。江水清浅。洞天开霁。恍若山灵护迎一行。及入莲台。林峦喷云。天风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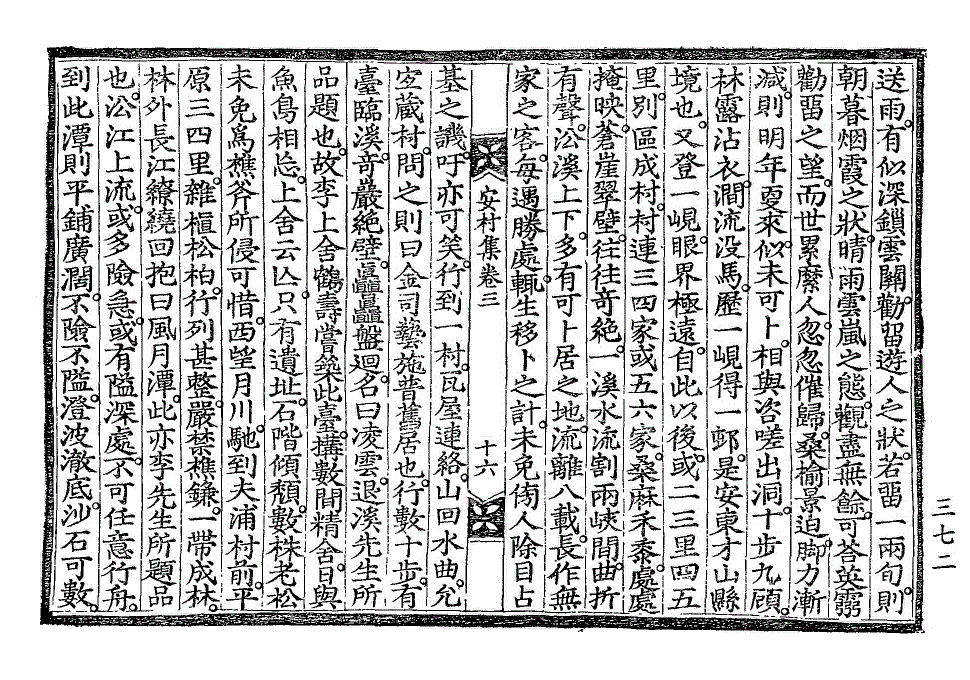 送雨。有似深锁云关。劝留游人之状。若留一两旬。则朝暮烟霞之状。晴雨云岚之态。观尽无馀。可答英灵劝留之望。而世累縻人。忽忽催归。桑榆景迫。脚力渐减。则明年更来。似未可卜。相与咨嗟出洞。十步九顾。林露沾衣。涧流没马。历一岘得一村。是安东才山县境也。又登一岘。眼界极远。自此以后。或二三里四五里。别区成村。村连三四家或五六家。桑麻禾黍。处处掩映。苍崖翠壁。往往奇绝。一溪水流割两峡间。曲折有声。沿溪上下。多有可卜居之地。流离八载。长作无家之客。每遇胜处。辄生移卜之计。未免傍人除目占基之讥。吁亦可笑。行到一村。瓦屋连络。山回水曲。允宜藏村。问之则曰金司艺施普旧居也。行数十步。有台临溪。奇岩绝壁。矗矗盘回。名曰凌云。退溪先生所品题也。故李上舍鹤寿尝筑此台。搆数间精舍。日与鱼鸟相忘。上舍云亡。只有遗址。石阶倾颓。数株老松未免为樵斧所侵可惜。西望月川。驰到夫浦村前。平原三四里。杂植松柏。行列甚整。严禁樵镰。一带成林。林外长江缭绕回抱曰风月潭。此亦李先生所题品也。沿江上流。或多险急。或有隘深处。不可任意行舟。到此潭则平铺广阔。不险不隘。澄波澈底。沙石可数。
送雨。有似深锁云关。劝留游人之状。若留一两旬。则朝暮烟霞之状。晴雨云岚之态。观尽无馀。可答英灵劝留之望。而世累縻人。忽忽催归。桑榆景迫。脚力渐减。则明年更来。似未可卜。相与咨嗟出洞。十步九顾。林露沾衣。涧流没马。历一岘得一村。是安东才山县境也。又登一岘。眼界极远。自此以后。或二三里四五里。别区成村。村连三四家或五六家。桑麻禾黍。处处掩映。苍崖翠壁。往往奇绝。一溪水流割两峡间。曲折有声。沿溪上下。多有可卜居之地。流离八载。长作无家之客。每遇胜处。辄生移卜之计。未免傍人除目占基之讥。吁亦可笑。行到一村。瓦屋连络。山回水曲。允宜藏村。问之则曰金司艺施普旧居也。行数十步。有台临溪。奇岩绝壁。矗矗盘回。名曰凌云。退溪先生所品题也。故李上舍鹤寿尝筑此台。搆数间精舍。日与鱼鸟相忘。上舍云亡。只有遗址。石阶倾颓。数株老松未免为樵斧所侵可惜。西望月川。驰到夫浦村前。平原三四里。杂植松柏。行列甚整。严禁樵镰。一带成林。林外长江缭绕回抱曰风月潭。此亦李先生所题品也。沿江上流。或多险急。或有隘深处。不可任意行舟。到此潭则平铺广阔。不险不隘。澄波澈底。沙石可数。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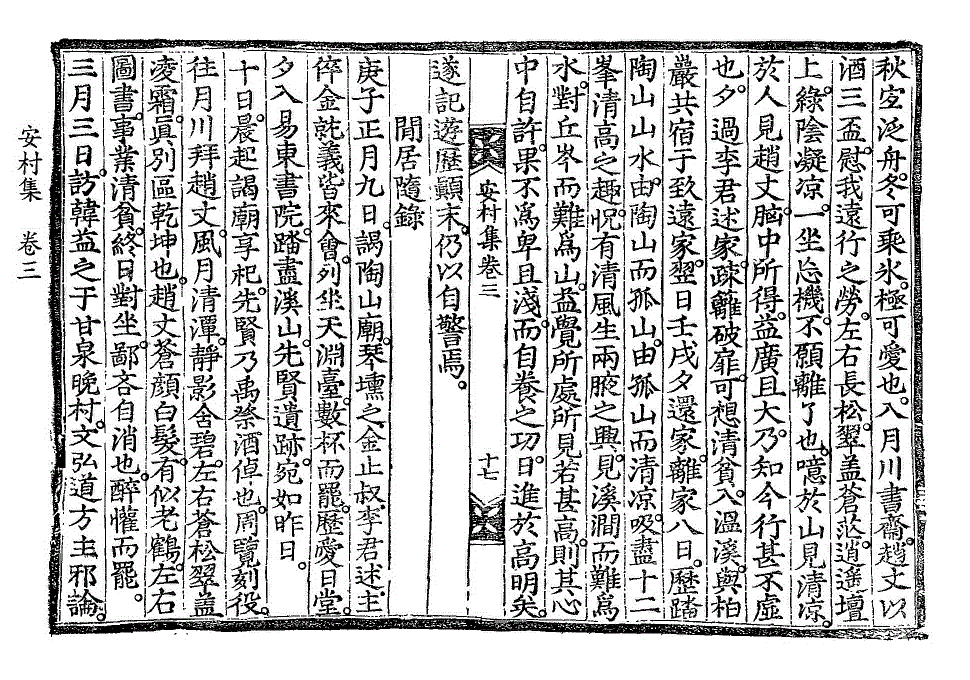 秋宜泛舟。冬可乘冰。极可爱也。入月川书斋。赵丈以酒三杯。慰我远行之劳。左右长松。翠盖苍茫。逍遥坛上。绿阴凝凉。一坐忘机。不愿离了也。噫于山见清凉。于人见赵丈。胸中所得。益广且大。乃知今行甚不虚也。夕过李君述家。疏篱破扉。可想清贫。入温溪。与柏岩共宿于致远家。翌日壬戌夕还家。离家八日。历踏陶山山水。由陶山而孤山。由孤山而清凉。吸尽十二峰清高之趣。恍有清风生两腋之兴。见溪涧而难为水。对丘岑而难为山。益觉所处所见若甚高。则其心中自许。果不为卑且浅。而自养之功。日进于高明矣。遂记游历颠末。仍以自警焉。
秋宜泛舟。冬可乘冰。极可爱也。入月川书斋。赵丈以酒三杯。慰我远行之劳。左右长松。翠盖苍茫。逍遥坛上。绿阴凝凉。一坐忘机。不愿离了也。噫于山见清凉。于人见赵丈。胸中所得。益广且大。乃知今行甚不虚也。夕过李君述家。疏篱破扉。可想清贫。入温溪。与柏岩共宿于致远家。翌日壬戌夕还家。离家八日。历踏陶山山水。由陶山而孤山。由孤山而清凉。吸尽十二峰清高之趣。恍有清风生两腋之兴。见溪涧而难为水。对丘岑而难为山。益觉所处所见若甚高。则其心中自许。果不为卑且浅。而自养之功。日进于高明矣。遂记游历颠末。仍以自警焉。閒居随录
庚子正月九日。谒陶山庙。琴埙之,金止叔,李君述,主倅金就义皆来会。列坐天渊台。数杯而罢。历爱日堂。夕入易东书院。踏尽溪山。先贤遗迹。宛如昨日。
十日。晨起谒庙享祀。先贤乃禹祭酒倬也。周览刻役。往月川拜赵丈。风月清潭。静影含碧。左右苍松翠盖凌霜。真别区乾坤也。赵丈苍颜白发。有似老鹤。左右图书。事业清贫。终日对坐。鄙吝自消也。醉欢而罢。
三月三日。访韩益之于甘泉晚村。文弘道方主邪论。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3L 页
 谋害朝绅。以益之贪虐之状。论启请拿。三启不允。论之不已。益之待命矣。噫小人之攻君子。自古有之。而狡诈险毒。做出无根之言。期于一网打尽。汲汲焉如恐不及。未有如今日者也。且北边胡人唐介。缔结元胡。将有大张之渐。南倭北胡夹作。有大举之计。莫此之忧。而徒事攻击同类。国之危亡可虑。痛哉奈何。
谋害朝绅。以益之贪虐之状。论启请拿。三启不允。论之不已。益之待命矣。噫小人之攻君子。自古有之。而狡诈险毒。做出无根之言。期于一网打尽。汲汲焉如恐不及。未有如今日者也。且北边胡人唐介。缔结元胡。将有大张之渐。南倭北胡夹作。有大举之计。莫此之忧。而徒事攻击同类。国之危亡可虑。痛哉奈何。五日。为吴大源所邀。终日醉话于夏寒亭。语及时事。时事专在李山海之手。山海交通金公亮。公亮乃金昭仪之甥也。昭仪方有宠于上。山海之事公亮有素矣。山海谪平海时。郑德远守宁海。相去密迩。与之交密。德远荐其门下文弘道。弘道性邪毒。逢迎山海之意。初拜正言。独启柳西厓。斥以奸邪忌克。妨贤病国。仍论西厓相知之人。纵恣无忌。朝廷谓台谏风棱。推戴为谋主。德远者赞弘道曰余两手不能长。不能拊弘道之背于千里京师也。大槩弘道之事。德远主张奖成。而其稍异于己者。则辄搆无根之言。必陷之于不测之地而后已。一时名望之人。皆荷担而预理踰岭之行。可谓痛心。山海初与柳西厓为腹心之交。每于昏夜。潜为出入。凡所举措。辄为问决。西厓知山海之粗鄙嗜利。交通宫禁。山海亦料西厓明知其事。而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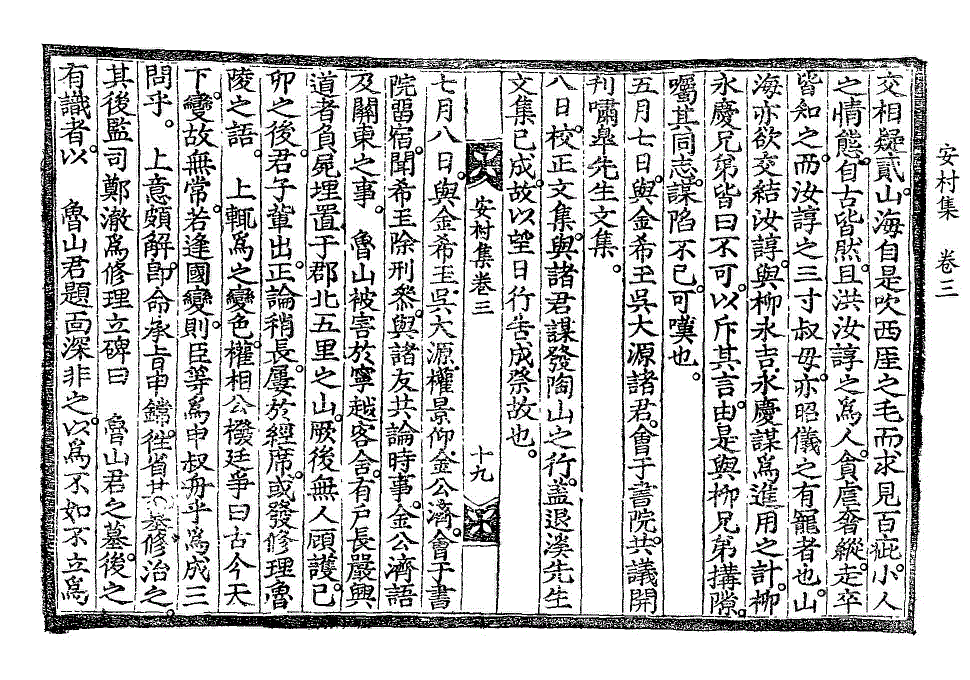 交相疑贰。山海自是吹西厓之毛。而求见百疵。小人之情态。自古皆然。且洪汝谆之为人。贪虐奢纵。走卒皆知之。而汝谆之三寸叔母。亦昭仪之有宠者也。山海亦欲交结汝谆。与柳永吉,永庆谋为进用之计。柳永庆兄弟皆曰不可。以斥其言。由是与柳兄弟搆隙。嘱其同志。谋陷不已。可叹也。
交相疑贰。山海自是吹西厓之毛。而求见百疵。小人之情态。自古皆然。且洪汝谆之为人。贪虐奢纵。走卒皆知之。而汝谆之三寸叔母。亦昭仪之有宠者也。山海亦欲交结汝谆。与柳永吉,永庆谋为进用之计。柳永庆兄弟皆曰不可。以斥其言。由是与柳兄弟搆隙。嘱其同志。谋陷不已。可叹也。五月七日。与金希玉,吴大源诸君。会于书院。共议开刊啸皋先生文集。
八日。校正文集。与诸君谋发陶山之行。盖退溪先生文集已成。故以望日行告成祭故也。
七月八日。与金希玉,吴大源,权景仰,金公济。会于书院留宿。闻希玉除刑参。与诸友共论时事。金公济语及关东之事。 鲁山被害于宁越客舍。有户长严兴道者负尸埋置于郡北五里之山。厥后无人顾护。己卯之后。君子辈出。正论稍长。屡于经席。或发修理鲁陵之语。 上辄为之变色。权相公橃廷争曰古今天下。变故无常。若逢国变。则臣等为申叔舟乎为成三问乎。 上意颇解。即命承旨申鋿。往省其墓修治之。其后监司郑澈为修理立碑曰 鲁山君之墓。后之有识者。 以鲁山君题面深非之。以为不如不立为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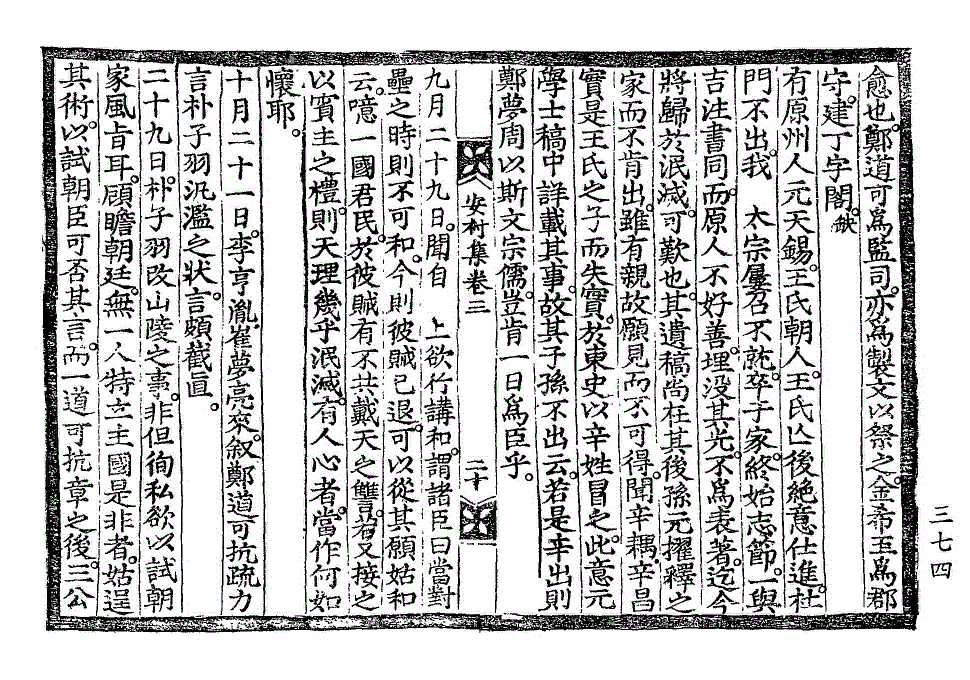 愈也。郑道可为监司。亦为制文以祭之。金希玉为郡守。建丁字阁。(缺)有原州人元天锡。王氏朝人。王氏亡后。绝意仕进。杜门不出。我 太宗屡召不就。卒于家。终始志节。一与吉注书同。而原人不好善。埋没其光。不为表著。迄今将归于泯灭。可叹也。其遗稿尚在其后孙元擢释之家而不肯出。虽有亲故愿见而不可得。闻辛祦,辛昌实是王氏之子而失实。于东史以辛姓冒之。此意元学士稿中详载其事。故其子孙不出云。若是辛出则郑梦周以斯文宗儒。岂肯一日为臣乎。
愈也。郑道可为监司。亦为制文以祭之。金希玉为郡守。建丁字阁。(缺)有原州人元天锡。王氏朝人。王氏亡后。绝意仕进。杜门不出。我 太宗屡召不就。卒于家。终始志节。一与吉注书同。而原人不好善。埋没其光。不为表著。迄今将归于泯灭。可叹也。其遗稿尚在其后孙元擢释之家而不肯出。虽有亲故愿见而不可得。闻辛祦,辛昌实是王氏之子而失实。于东史以辛姓冒之。此意元学士稿中详载其事。故其子孙不出云。若是辛出则郑梦周以斯文宗儒。岂肯一日为臣乎。九月二十九日。闻自 上欲行讲和。谓诸臣曰当对垒之时则不可和。今则彼贼已退。可以从其愿姑和云。噫一国君民。于彼贼有不共戴天之雠。若又接之以宾主之礼。则天理几乎泯灭。有人心者。当作何如怀耶。
十月二十一日。李亨胤,崔梦亮来。叙郑道可抗疏力言朴子羽汎滥之状。言颇截直。
二十九日。朴子羽改山陵之事。非但徇私欲以试朝家风旨耳。顾瞻朝廷。无一人特立主国是非者。姑逞其术。以试朝臣可否其言。而一道可抗章之后。三公
安村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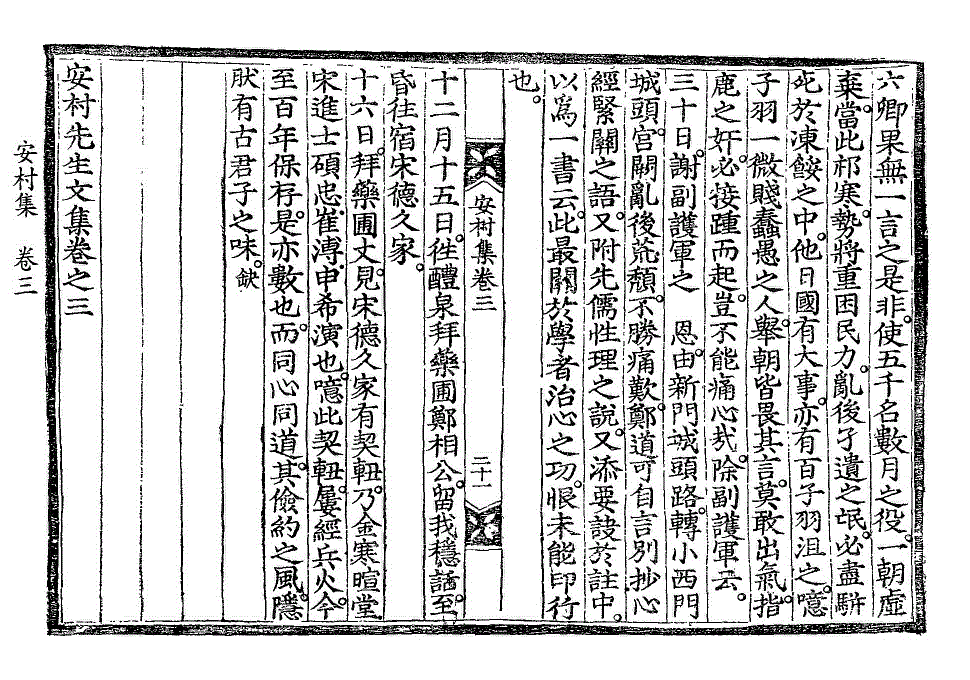 六卿果无一言之是非。使五千名数月之役。一朝虚弃。当此祁寒。势将重困民力。乱后孑遗之氓。必尽骈死于冻馁之中。他日国有大事。亦有百子羽沮之。噫子羽一微贱蠢愚之人。举朝皆畏其言。莫敢出气。指鹿之奸。必接踵而起。岂不能痛心哉。除副护军云。
六卿果无一言之是非。使五千名数月之役。一朝虚弃。当此祁寒。势将重困民力。乱后孑遗之氓。必尽骈死于冻馁之中。他日国有大事。亦有百子羽沮之。噫子羽一微贱蠢愚之人。举朝皆畏其言。莫敢出气。指鹿之奸。必接踵而起。岂不能痛心哉。除副护军云。三十日。谢副护军之 恩。由新门城头路。转小西门城头。宫阙乱后荒颓。不胜痛叹。郑道可自言别抄心经紧关之语。又附先儒性理之说。又添要诀于注中。以为一书云。此最关于学者治心之功。恨未能印行也。
十二月十五日。往醴泉拜药圃郑相公。留我稳话。至昏往宿宋德久家。
十六日。拜药圃丈。见宋德久家有契轴。乃金寒暄堂,宋进士硕忠,崔溥,申希演也。噫此契轴。屡经兵火。今至百年保存。是亦数也。而同心同道。其俭约之风。隐肰有古君子之味。(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