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x 页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记
记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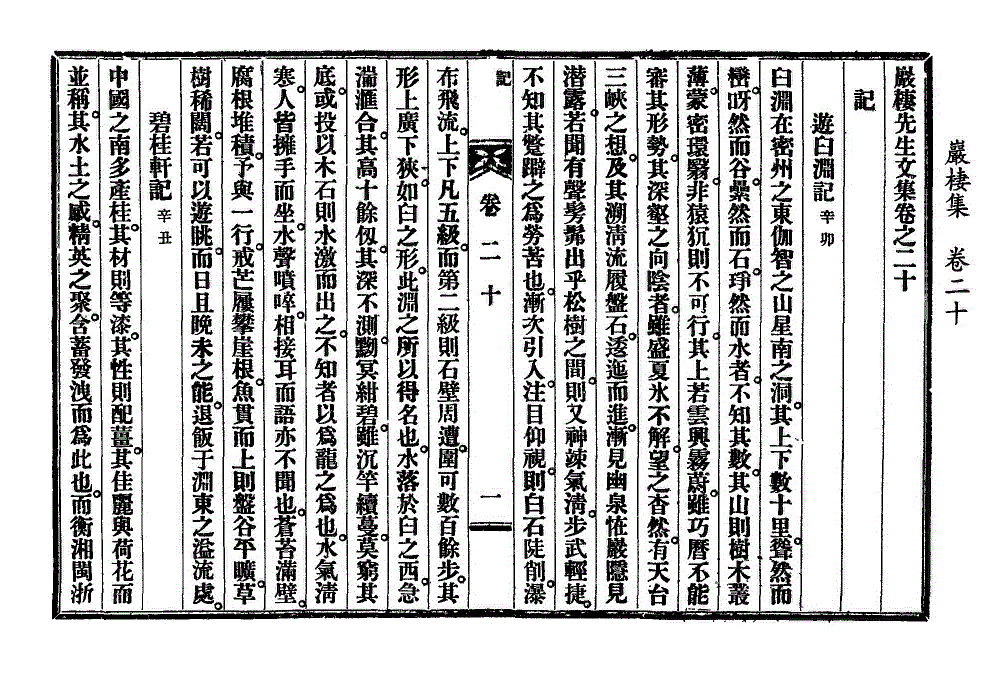 游臼渊记(辛卯)
游臼渊记(辛卯)臼渊在密州之东伽智之山星南之洞。其上下数十里。耸然而峦。呀然而谷。累然而石。琤然而水者。不知其数。其山则树木丛薄。蒙密环翳。非猿
碧桂轩记(辛丑)
中国之南多产桂。其材则等漆。其性则配姜。其佳丽与荷花而并称。其水土之感。精英之聚。含蓄发泄而为此也。而衡湘闽浙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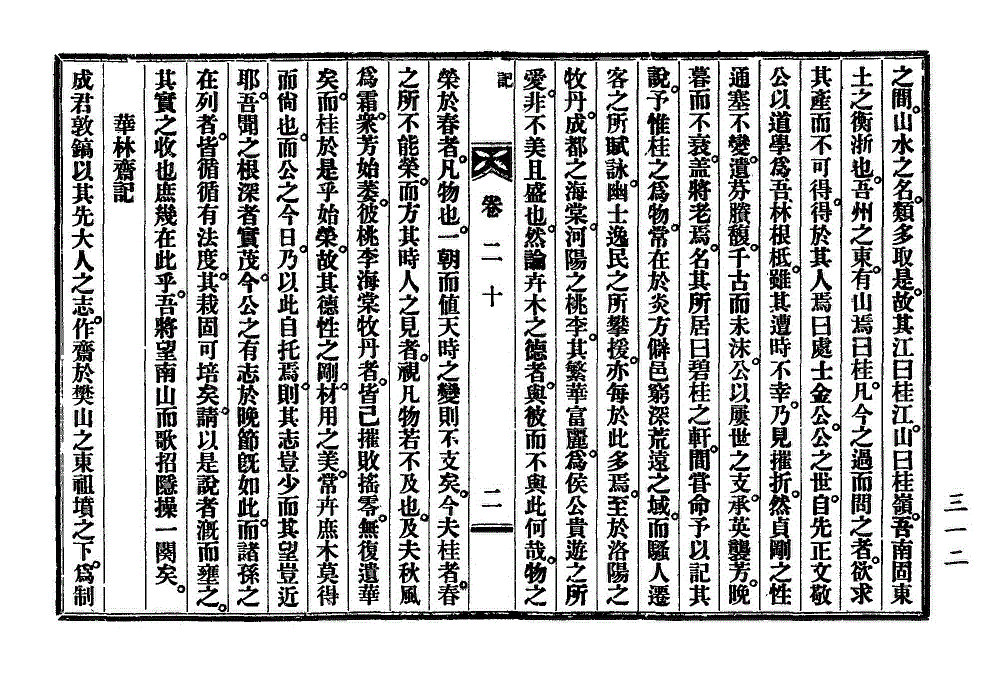 之间。山水之名。类多取是。故其江曰桂江。山曰桂岭。吾南固东土之衡浙也。吾州之东。有山焉曰桂。凡今之过而问之者。欲求其产而不可得。得于其人焉曰处士金公。公之世。自先正文敬公以道学为吾林根柢。虽其遭时不幸。乃见摧折。然贞刚之性通塞不变。遗芬剩馥。千古而未沫。公以屡世之支。承英袭芳。晚暮而不衰。盖将老焉。名其所居曰碧桂之轩。间尝命予以记其说。予惟桂之为物。常在于炎方僻邑穷深荒远之域。而骚人迁客之所赋咏。幽士逸民之所攀援。亦每于此多焉。至于洛阳之牧丹。成都之海棠。河阳之桃李。其繁华富丽。为侯公贵游之所爱。非不美且盛也。然论卉木之德者。与彼而不与此何哉。物之荣于春者。凡物也。一朝而值天时之变则不支矣。今夫桂者。春之所不能荣。而方其时人之见者。视凡物若不及也。及夫秋风为霜。众芳始萎。彼桃李海棠牧丹者。皆已摧败摇零。无复遗华矣。而桂于是乎始荣。故其德性之刚。材用之美。常卉庶木莫得而尚也。而公之今日。乃以此自托焉。则其志岂少而其望岂近耶。吾闻之根深者实茂。今公之有志于晚节既如此。而诸孙之在列者。皆循循有法度。其栽固可培矣。请以是说者溉而壅之。其实之收也庶几在此乎。吾将望南山而歌招隐操一阕矣。
之间。山水之名。类多取是。故其江曰桂江。山曰桂岭。吾南固东土之衡浙也。吾州之东。有山焉曰桂。凡今之过而问之者。欲求其产而不可得。得于其人焉曰处士金公。公之世。自先正文敬公以道学为吾林根柢。虽其遭时不幸。乃见摧折。然贞刚之性通塞不变。遗芬剩馥。千古而未沫。公以屡世之支。承英袭芳。晚暮而不衰。盖将老焉。名其所居曰碧桂之轩。间尝命予以记其说。予惟桂之为物。常在于炎方僻邑穷深荒远之域。而骚人迁客之所赋咏。幽士逸民之所攀援。亦每于此多焉。至于洛阳之牧丹。成都之海棠。河阳之桃李。其繁华富丽。为侯公贵游之所爱。非不美且盛也。然论卉木之德者。与彼而不与此何哉。物之荣于春者。凡物也。一朝而值天时之变则不支矣。今夫桂者。春之所不能荣。而方其时人之见者。视凡物若不及也。及夫秋风为霜。众芳始萎。彼桃李海棠牧丹者。皆已摧败摇零。无复遗华矣。而桂于是乎始荣。故其德性之刚。材用之美。常卉庶木莫得而尚也。而公之今日。乃以此自托焉。则其志岂少而其望岂近耶。吾闻之根深者实茂。今公之有志于晚节既如此。而诸孙之在列者。皆循循有法度。其栽固可培矣。请以是说者溉而壅之。其实之收也庶几在此乎。吾将望南山而歌招隐操一阕矣。华林斋记
成君敦镐以其先大人之志。作斋于樊山之东祖坟之下。为制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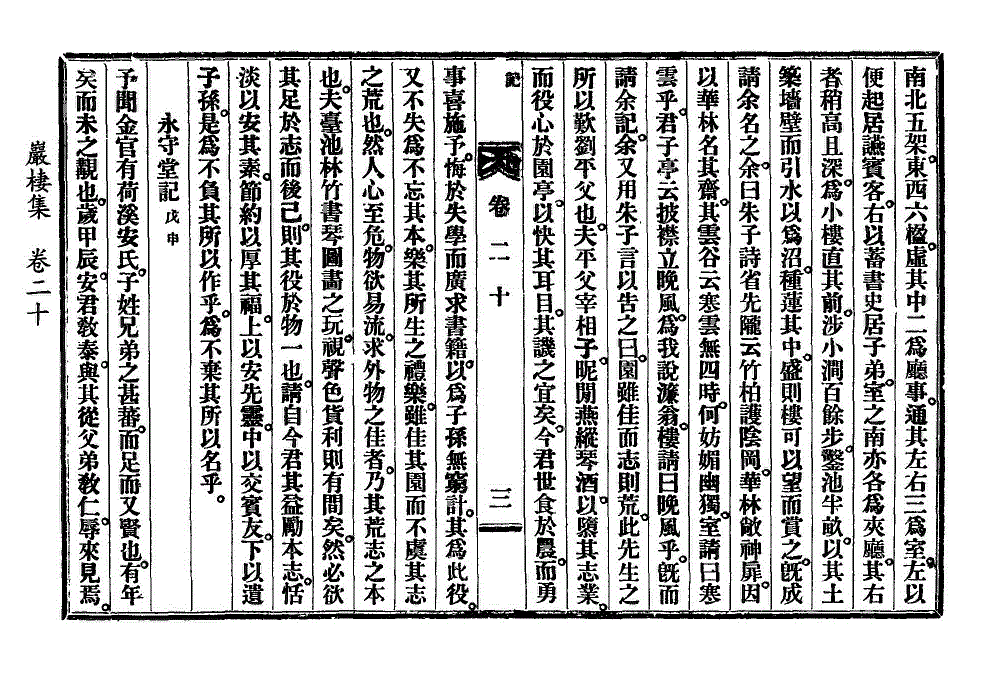 南北五架。东西六楹。虚其中二为厅事。通其左右三为室。左以便起居宴宾客。右以蓄书史居子弟。室之南亦各为夹厅。其右者稍高且深。为小楼直其前。涉小涧百馀步。凿池半亩。以其土筑墙壁而引水以为沼。种莲其中。盛则楼可以望而赏之。既成请余名之。余曰朱子诗省先陇云竹柏护阴冈。华林敞神扉。因以华林名其斋。其云谷云寒云无四时。何妨媚幽独。室请曰寒云乎。君子亭云披襟立晚风。为我说濂翁。楼请曰晚风乎。既而请余记。余又用朱子言以告之曰。园虽佳而志则荒。此先生之所以叹刘平父也。夫平父宰相子。昵閒燕纵琴酒。以隳其志业。而役心于园亭。以快其耳目。其讥之宜矣。今君世食于农。而勇事喜施予。悔于失学而广求书籍。以为子孙无穷计。其为此役。又不失为不忘其本。乐其所生之礼乐。虽佳其园而不虞其志之荒也。然人心至危。物欲易流。求外物之佳者。乃其荒志之本也。夫台池林竹书琴图画之玩。视声色货利则有间矣。然必欲其足于志而后已。则其役于物一也。请自今君其益励本志。恬淡以安其素。节约以厚其福。上以安先灵。中以交宾友。下以遗子孙。是为不负其所以作乎。为不弃其所以名乎。
南北五架。东西六楹。虚其中二为厅事。通其左右三为室。左以便起居宴宾客。右以蓄书史居子弟。室之南亦各为夹厅。其右者稍高且深。为小楼直其前。涉小涧百馀步。凿池半亩。以其土筑墙壁而引水以为沼。种莲其中。盛则楼可以望而赏之。既成请余名之。余曰朱子诗省先陇云竹柏护阴冈。华林敞神扉。因以华林名其斋。其云谷云寒云无四时。何妨媚幽独。室请曰寒云乎。君子亭云披襟立晚风。为我说濂翁。楼请曰晚风乎。既而请余记。余又用朱子言以告之曰。园虽佳而志则荒。此先生之所以叹刘平父也。夫平父宰相子。昵閒燕纵琴酒。以隳其志业。而役心于园亭。以快其耳目。其讥之宜矣。今君世食于农。而勇事喜施予。悔于失学而广求书籍。以为子孙无穷计。其为此役。又不失为不忘其本。乐其所生之礼乐。虽佳其园而不虞其志之荒也。然人心至危。物欲易流。求外物之佳者。乃其荒志之本也。夫台池林竹书琴图画之玩。视声色货利则有间矣。然必欲其足于志而后已。则其役于物一也。请自今君其益励本志。恬淡以安其素。节约以厚其福。上以安先灵。中以交宾友。下以遗子孙。是为不负其所以作乎。为不弃其所以名乎。永守堂记(戊申)
予闻金官有荷溪安氏。子姓兄弟之甚蕃。而足而又贤也。有年矣而未之觏也。岁甲辰。安君教泰。与其从父弟教仁。辱来见焉。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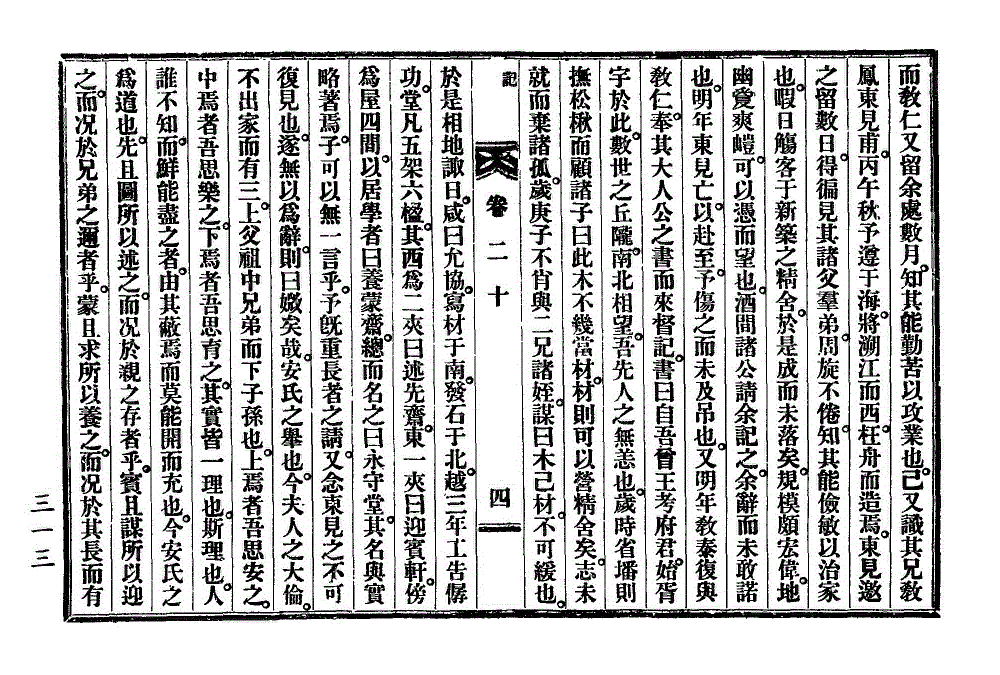 而教仁又留余处数月。知其能勤苦以攻业也。已又识其兄教凤东见甫。丙午秋予遵于海。将溯江而西。枉舟而造焉。东见邀之留数日。得遍见其诸父群弟。周旋不倦。知其能俭敏以治家也。暇日觞客于新筑之精舍。于是成而未落矣。规模颇宏伟。地幽夐爽嵦。可以凭而望也。酒间诸公请余记之。余辞而未敢诺也。明年东见亡。以赴至。予伤之而未及吊也。又明年教泰复与教仁。奉其大人公之书而来督记。书曰自吾曾王考府君。始胥宇于此。数世之丘陇。南北相望。吾先人之无恙也。岁时省墦则抚松楸而顾诸子曰此木不几当材。材则可以营精舍矣。志未就而弃诸孤。岁庚子不肖与二兄诸侄。谋曰木已材。不可缓也。于是相地诹日。咸曰允协。写材于南。发石于北。越三年工告僝功。堂凡五架六楹。其西为二夹曰述先斋。东一夹曰迎宾轩。傍为屋四间。以居学者曰养蒙斋。总而名之曰永守堂。其名与实略著焉。子可以无一言乎。予既重长者之请。又念东见之不可复见也。遂无以为辞。则曰美矣哉。安氏之举也。今夫人之大伦。不出家而有三。上父祖中兄弟而下子孙也。上焉者吾思安之。中焉者吾思乐之。下焉者吾思育之。其实皆一理也。斯理也。人谁不知。而鲜能尽之者。由其蔽焉而莫能开而充也。今安氏之为道也。先且图所以述之。而况于亲之存者乎。宾且谋所以迎之。而况于兄弟之迩者乎。蒙且求所以养之。而况于其长而有
而教仁又留余处数月。知其能勤苦以攻业也。已又识其兄教凤东见甫。丙午秋予遵于海。将溯江而西。枉舟而造焉。东见邀之留数日。得遍见其诸父群弟。周旋不倦。知其能俭敏以治家也。暇日觞客于新筑之精舍。于是成而未落矣。规模颇宏伟。地幽夐爽嵦。可以凭而望也。酒间诸公请余记之。余辞而未敢诺也。明年东见亡。以赴至。予伤之而未及吊也。又明年教泰复与教仁。奉其大人公之书而来督记。书曰自吾曾王考府君。始胥宇于此。数世之丘陇。南北相望。吾先人之无恙也。岁时省墦则抚松楸而顾诸子曰此木不几当材。材则可以营精舍矣。志未就而弃诸孤。岁庚子不肖与二兄诸侄。谋曰木已材。不可缓也。于是相地诹日。咸曰允协。写材于南。发石于北。越三年工告僝功。堂凡五架六楹。其西为二夹曰述先斋。东一夹曰迎宾轩。傍为屋四间。以居学者曰养蒙斋。总而名之曰永守堂。其名与实略著焉。子可以无一言乎。予既重长者之请。又念东见之不可复见也。遂无以为辞。则曰美矣哉。安氏之举也。今夫人之大伦。不出家而有三。上父祖中兄弟而下子孙也。上焉者吾思安之。中焉者吾思乐之。下焉者吾思育之。其实皆一理也。斯理也。人谁不知。而鲜能尽之者。由其蔽焉而莫能开而充也。今安氏之为道也。先且图所以述之。而况于亲之存者乎。宾且谋所以迎之。而况于兄弟之迩者乎。蒙且求所以养之。而况于其长而有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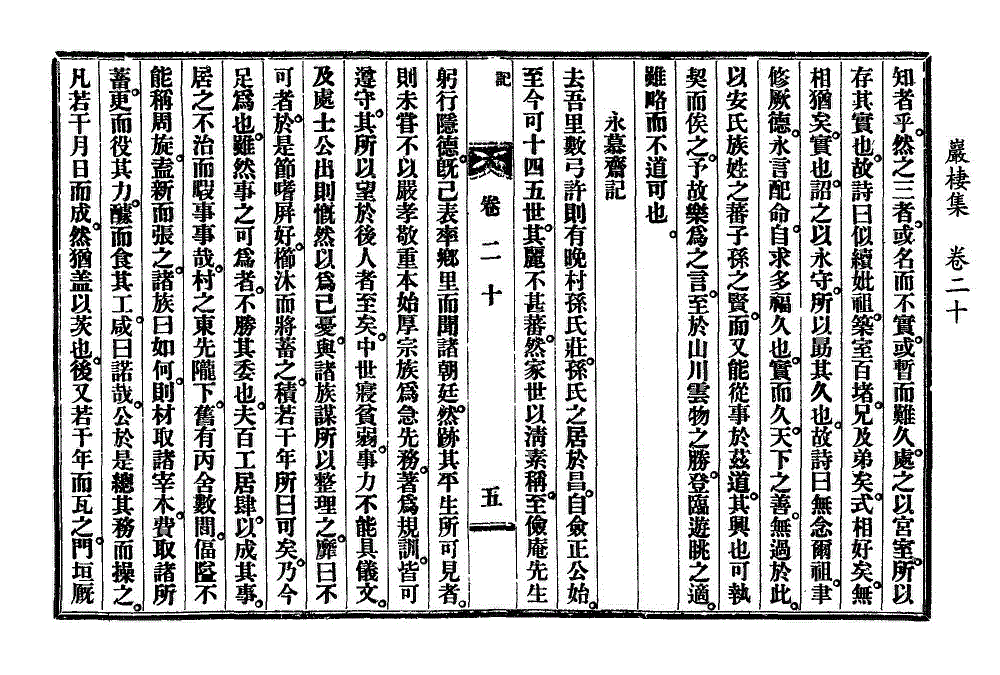 知者乎。然之三者。或名而不实。或暂而难久。处之以宫室。所以存其实也。故诗曰似续妣祖。筑室百堵。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实也。诏之以永守。所以勖其久也。故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久也。实而久。天下之善。无过于此。以安氏族姓之蕃子孙之贤。而又能从事于兹道。其兴也可执契而俟之。予故乐为之言。至于山川云物之胜。登临游眺之适。虽略而不道可也。
知者乎。然之三者。或名而不实。或暂而难久。处之以宫室。所以存其实也。故诗曰似续妣祖。筑室百堵。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实也。诏之以永守。所以勖其久也。故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久也。实而久。天下之善。无过于此。以安氏族姓之蕃子孙之贤。而又能从事于兹道。其兴也可执契而俟之。予故乐为之言。至于山川云物之胜。登临游眺之适。虽略而不道可也。永慕斋记
去吾里数弓许则有晚村孙氏庄。孙氏之居于昌。自佥正公始。至今可十四五世。其丽不甚蕃。然家世以清素称。至俭庵先生躬行隐德。既已表率乡里而闻诸朝廷。然迹其平生所可见者。则未尝不以严孝敬重本始厚宗族为急先务。著为规训。皆可遵守。其所以望于后人者至矣。中世寝贫弱。事力不能具仪文。及处士公出则慨然以为己忧。与诸族谋所以整理之。靡曰不可者。于是节嗜屏好。栉沐而将蓄之。积若干年所曰可矣。乃今足为也。虽然事之可为者。不胜其委也。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居之不治而暇事事哉。村之东先陇下。旧有丙舍数间。偪隘不能称周旋。盍新而张之。诸族曰如何。则材取诸宰木。费取诸所蓄。更而役其力。醵而食其工。咸曰诺哉。公于是总其务而操之。凡若干月日而成。然犹盖以茨也。后又若干年而瓦之。门垣厩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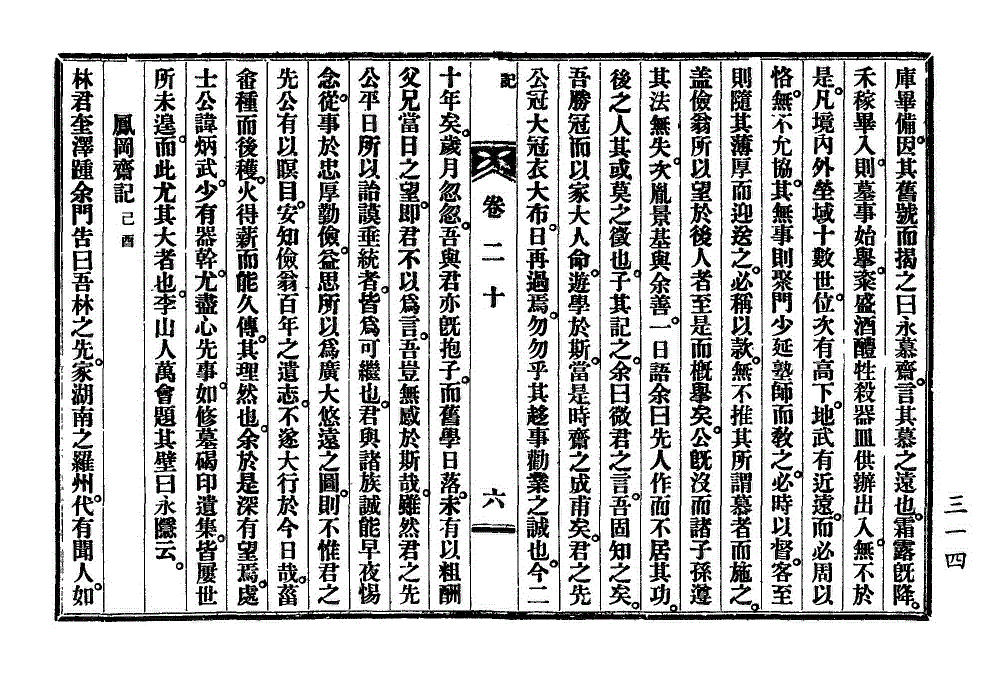 库毕备。因其旧号而揭之曰永慕斋。言其慕之远也。霜露既降。禾稼毕入。则墓事始举。粢盛酒醴牲杀器皿供办出入。无不于是。凡境内外茔域十数世。位次有高下。地武有近远。而必周以恪。无不允协。其无事则聚门少延塾师而教之。必时以督。客至则随其薄厚而迎送之。必称以款。无不推其所谓慕者而施之。盖俭翁所以望于后人者至是而概举矣。公既没而诸子孙遵其法无失。次胤景基与余善。一日语余曰先人作而不居其功。后之人其或莫之徵也。子其记之。余曰微君之言。吾固知之矣。吾胜冠而以家大人命。游学于斯。当是时斋之成甫矣。君之先公冠大冠衣大布。日再过焉。勿勿乎其趍事劝业之诚也。今二十年矣。岁月忽忽。吾与君亦既抱子。而旧学日落。未有以粗酬父兄当日之望。即君不以为言。吾岂无感于斯哉。虽然君之先公平日所以诒谟垂统者。皆为可继也。君与诸族诚能早夜惕念。从事于忠厚勤俭。益思所以为广大悠远之图。则不惟君之先公有以瞑目。安知俭翁百年之遗志。不遂大行于今日哉。菑畬种而后穫。火得薪而能久传。其理然也。余于是深有望焉。处士公讳炳武。少有器干。尤尽心先事。如修墓碣印遗集。皆屡世所未遑。而此尤其大者也。李山人万会题其壁曰永隐云。
库毕备。因其旧号而揭之曰永慕斋。言其慕之远也。霜露既降。禾稼毕入。则墓事始举。粢盛酒醴牲杀器皿供办出入。无不于是。凡境内外茔域十数世。位次有高下。地武有近远。而必周以恪。无不允协。其无事则聚门少延塾师而教之。必时以督。客至则随其薄厚而迎送之。必称以款。无不推其所谓慕者而施之。盖俭翁所以望于后人者至是而概举矣。公既没而诸子孙遵其法无失。次胤景基与余善。一日语余曰先人作而不居其功。后之人其或莫之徵也。子其记之。余曰微君之言。吾固知之矣。吾胜冠而以家大人命。游学于斯。当是时斋之成甫矣。君之先公冠大冠衣大布。日再过焉。勿勿乎其趍事劝业之诚也。今二十年矣。岁月忽忽。吾与君亦既抱子。而旧学日落。未有以粗酬父兄当日之望。即君不以为言。吾岂无感于斯哉。虽然君之先公平日所以诒谟垂统者。皆为可继也。君与诸族诚能早夜惕念。从事于忠厚勤俭。益思所以为广大悠远之图。则不惟君之先公有以瞑目。安知俭翁百年之遗志。不遂大行于今日哉。菑畬种而后穫。火得薪而能久传。其理然也。余于是深有望焉。处士公讳炳武。少有器干。尤尽心先事。如修墓碣印遗集。皆屡世所未遑。而此尤其大者也。李山人万会题其壁曰永隐云。凤冈斋记(己酉)
林君奎泽踵余门告曰吾林之先。家湖南之罗州。代有闻人。如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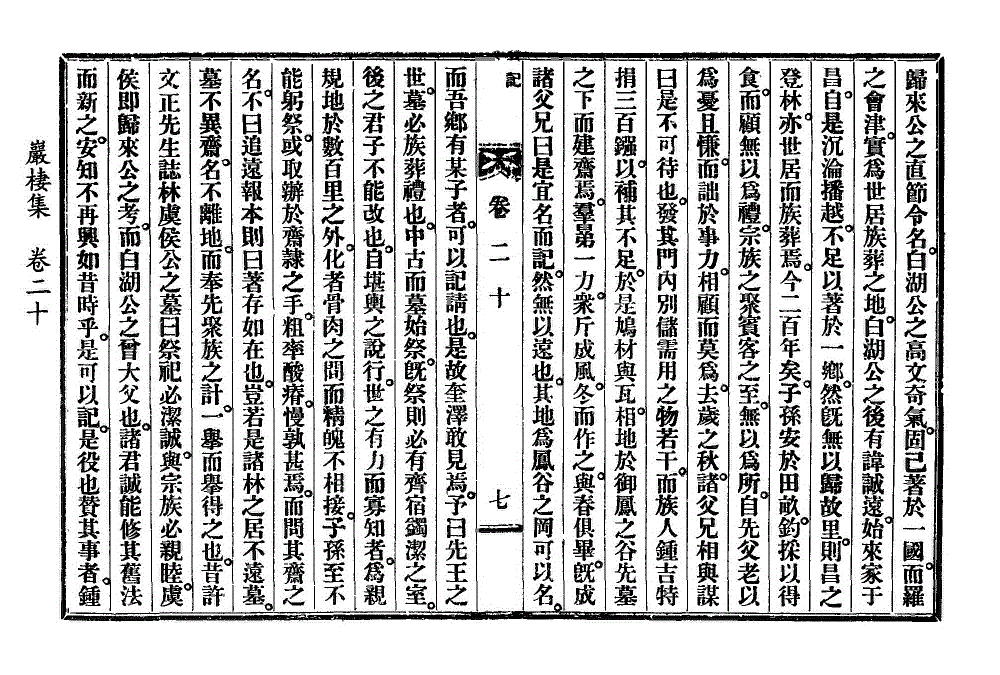 归来公之直节令名。白湖公之高文奇气。固已著于一国。而罗之会津。实为世居族葬之地。白湖公之后有讳诚远。始来家于昌。自是沉沦播越。不足以著于一乡。然既无以归故里。则昌之登林。亦世居而族葬焉。今二百年矣。子孙安于田亩。钓采以得食。而顾无以为礼。宗族之聚宾客之至。无以为所。自先父老以为忧且慊。而诎于事力。相顾而莫为。去岁之秋。诸父兄相与谋曰是不可待也。发其门内别储需用之物若干。而族人钟吉特捐三百镪。以补其不足。于是鸠材与瓦。相地于御凤之谷先墓之下而建斋焉。群昆一力。众斤成风。冬而作之。与春俱毕。既成诸父兄曰是宜名而记。然无以远也。其地为凤谷之冈可以名。而吾乡有某子者。可以记请也。是故奎泽敢见焉。予曰先王之世。墓必族葬礼也。中古而墓始祭。既祭则必有齐宿蠲洁之室。后之君子不能改也。自堪舆之说行。世之有力而寡知者。为亲规地于数百里之外。化者骨肉之间而精魄不相接。子孙至不能躬祭。或取办于斋隶之手。粗率酸瘠。慢孰甚焉。而问其斋之名。不曰追远报本则曰著存如在也。岂若是诸林之居不远墓。墓不异斋。名不离地。而奉先聚族之计。一举而举得之也。昔许文正先生志林虞侯公之墓曰祭祀必洁诚。与宗族必亲睦。虞侯即归来公之考。而白湖公之曾大父也。诸君诚能修其旧法而新之。安知不再兴如昔时乎。是可以记。是役也赞其事者。钟
归来公之直节令名。白湖公之高文奇气。固已著于一国。而罗之会津。实为世居族葬之地。白湖公之后有讳诚远。始来家于昌。自是沉沦播越。不足以著于一乡。然既无以归故里。则昌之登林。亦世居而族葬焉。今二百年矣。子孙安于田亩。钓采以得食。而顾无以为礼。宗族之聚宾客之至。无以为所。自先父老以为忧且慊。而诎于事力。相顾而莫为。去岁之秋。诸父兄相与谋曰是不可待也。发其门内别储需用之物若干。而族人钟吉特捐三百镪。以补其不足。于是鸠材与瓦。相地于御凤之谷先墓之下而建斋焉。群昆一力。众斤成风。冬而作之。与春俱毕。既成诸父兄曰是宜名而记。然无以远也。其地为凤谷之冈可以名。而吾乡有某子者。可以记请也。是故奎泽敢见焉。予曰先王之世。墓必族葬礼也。中古而墓始祭。既祭则必有齐宿蠲洁之室。后之君子不能改也。自堪舆之说行。世之有力而寡知者。为亲规地于数百里之外。化者骨肉之间而精魄不相接。子孙至不能躬祭。或取办于斋隶之手。粗率酸瘠。慢孰甚焉。而问其斋之名。不曰追远报本则曰著存如在也。岂若是诸林之居不远墓。墓不异斋。名不离地。而奉先聚族之计。一举而举得之也。昔许文正先生志林虞侯公之墓曰祭祀必洁诚。与宗族必亲睦。虞侯即归来公之考。而白湖公之曾大父也。诸君诚能修其旧法而新之。安知不再兴如昔时乎。是可以记。是役也赞其事者。钟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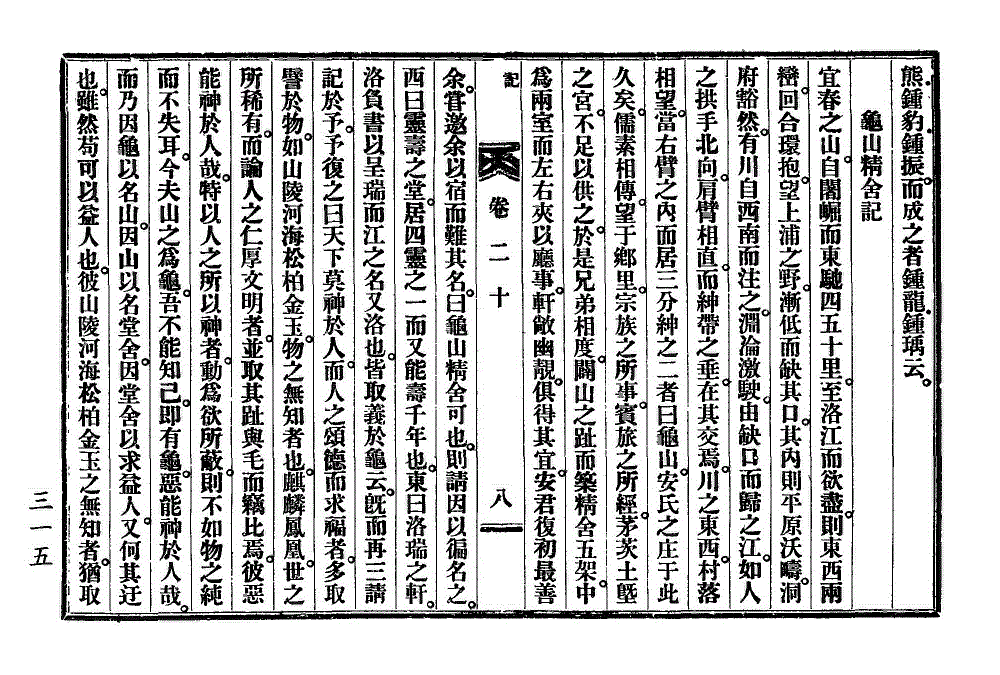 熊,钟豹,钟振。而成之者钟龙,钟瑀云。
熊,钟豹,钟振。而成之者钟龙,钟瑀云。龟山精舍记
宜春之山。自阇崛而东驰四五十里。至洛江而欲尽。则东西两峦。回合环抱。望上浦之野。渐低而缺其口。其内则平原沃畴。洞府豁然。有川自西南而注之。渊沦激驶。由缺口而归之江。如人之拱手北向。肩臂相直。而绅带之垂。在其交焉。川之东西。村落相望。当右臂之内而居三分绅之二者曰龟山。安氏之庄于此久矣。儒素相传。望于乡里。宗族之所事。宾旅之所经。茅茨土塈之宫。不足以供之。于是兄弟相度。辟山之趾而筑精舍五架。中为两室而左右夹以厅事。轩敞幽靓。俱得其宜。安君复初最善余。尝邀余以宿而难其名。曰龟山精舍可也。则请因以遍名之。西曰灵寿之堂。居四灵之一而又能寿千年也。东曰洛瑞之轩。洛负书以呈瑞而江之名又洛也。皆取义于龟云。既而再三请记于予。予复之曰天下莫神于人。而人之颂德而求福者。多取譬于物。如山陵河海松柏金玉。物之无知者也。麒麟凤凰。世之所稀有。而论人之仁厚文明者。并取其趾与毛而窃比焉。彼恶能神于人哉。特以人之所以神者。动为欲所蔽。则不如物之纯而不失耳。今夫山之为龟。吾不能知已。即有龟。恶能神于人哉。而乃因龟以名山。因山以名堂舍。因堂舍以求益人。又何其迂也。虽然苟可以益人也。彼山陵河海松柏金玉之无知者。犹取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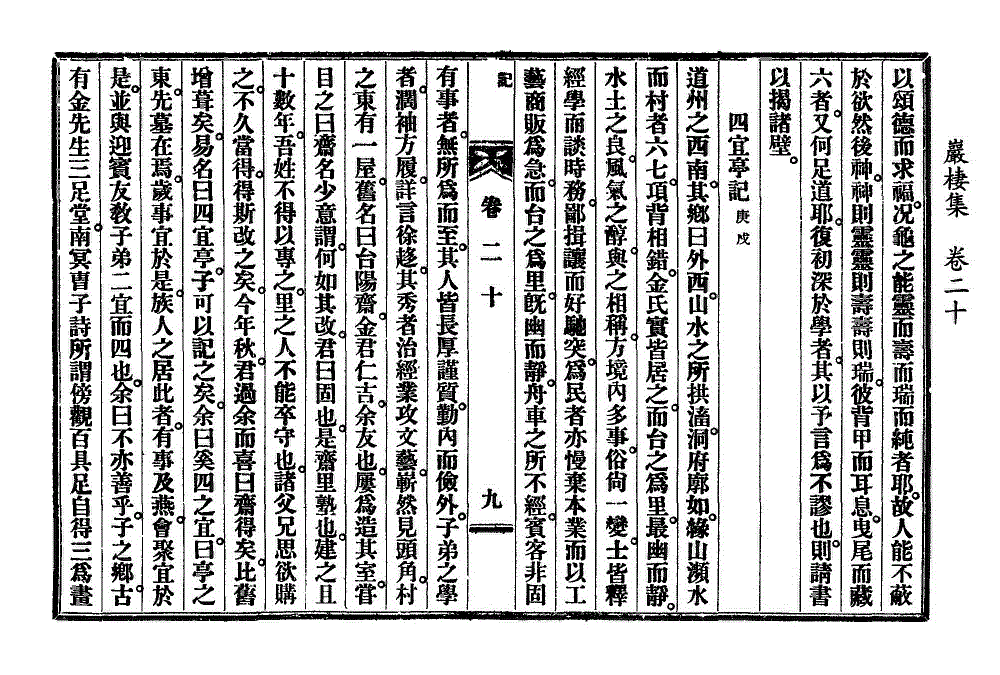 以颂德而求福。况龟之能灵而寿而瑞而纯者耶。故人能不蔽于欲然后神。神则灵灵则寿寿则瑞。彼背甲而耳息。曳尾而藏六者。又何足道耶。复初深于学者。其以予言为不谬也。则请书以揭诸壁。
以颂德而求福。况龟之能灵而寿而瑞而纯者耶。故人能不蔽于欲然后神。神则灵灵则寿寿则瑞。彼背甲而耳息。曳尾而藏六者。又何足道耶。复初深于学者。其以予言为不谬也。则请书以揭诸壁。四宜亭记(庚戌)
道州之西南。其乡曰外西。山水之所拱滀。洞府廓如。缘山濒水而村者六七。项背相错。金氏实皆居之。而台之为里。最幽而静。水土之良。风气之醇。与之相称。方境内多事。俗尚一变。士皆释经学而谈时务。鄙揖让而好驰突。为民者亦慢弃本业而以工艺商贩为急。而台之为里。既幽而静。舟车之所不经。宾客非固有事者。无所为而至。其人皆长厚谨质。勤内而俭外。子弟之学者。阔袖方履。详言徐趍。其秀者治经业攻文艺。崭然见头角。村之东有一屋。旧名曰台阳斋。金君仁吉。余友也。屡为造其室。尝目之曰斋名少意谓。何如其改。君曰固也。是斋里塾也。建之且十数年。吾姓不得以专之。里之人不能卒守也。诸父兄思欲购之。不久当得。得斯改之矣。今年秋。君过余而喜曰斋得矣。比旧增葺矣。易名曰四宜亭。子可以记之矣。余曰奚四之宜。曰亭之东。先墓在焉。岁事宜于是。族人之居此者。有事及燕。会聚宜于是。并与迎宾友教子弟二宜而四也。余曰不亦善乎。子之乡。古有金先生三足堂。南冥曹子诗所谓傍观百具足自得三为画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6L 页
 是也。夫天下之宜。不可以限之也。吾子志乎古者。而父兄之所愿子弟之所事。事无大小。苟近于不宜者则不为也。如此虽曰百宜。何所不可。而必止于四者。岂亦以自得为画者欤。昔鳌城李相公慕三足之风。而恨其不能得。夫以一国之名相而以不得为恨。则其高诚未易言也。若乃四者之宜则日用之常。无足为高。然能充其名。非志出乎今人而行合乎古人者。亦未易及也。余今病且倦矣。思欲学南冥子一赋于子之亭而不可得矣。吾子勉之。百世之后。使斯亭与三足堂并称。如鳌城公者慕而愿之可也。
是也。夫天下之宜。不可以限之也。吾子志乎古者。而父兄之所愿子弟之所事。事无大小。苟近于不宜者则不为也。如此虽曰百宜。何所不可。而必止于四者。岂亦以自得为画者欤。昔鳌城李相公慕三足之风。而恨其不能得。夫以一国之名相而以不得为恨。则其高诚未易言也。若乃四者之宜则日用之常。无足为高。然能充其名。非志出乎今人而行合乎古人者。亦未易及也。余今病且倦矣。思欲学南冥子一赋于子之亭而不可得矣。吾子勉之。百世之后。使斯亭与三足堂并称。如鳌城公者慕而愿之可也。追远斋重修记(癸丑)
孔子之乡曰曲阜。里曰阙里。所葬曰孔林。在鲁城北泗水上。嫡嗣世袭。为衍圣公。当元顺帝时。孔子五十三世孙浣生二子。长曰思晦。亦袭封。次曰绍。以翰林学士。东出事高丽恭悯王。位至门下侍郎封桧原君。今昌原府西斗尺山枕坎之原。有大封焉。公之墓也。至公孙有曰渔村俯,孤山𠋎。皆为丽末闻人。厥后子孙散处一国。皆以昌原为贯。以二公为祖。至我 正庙大欲崇孔氏。尝 幸水原。得渔村后孙文献公瑞麟旧墟。升为阙里。 命立祠祀夫子。且 谕使燕臣购阙里图谱以来。于是 命诸孔氏。改贯曲阜。呜乎。 圣王之爱圣人之后。若是其至也。而独不及于公之墓何哉。意者其荒远处僻。刺史守令不以闻欤。孔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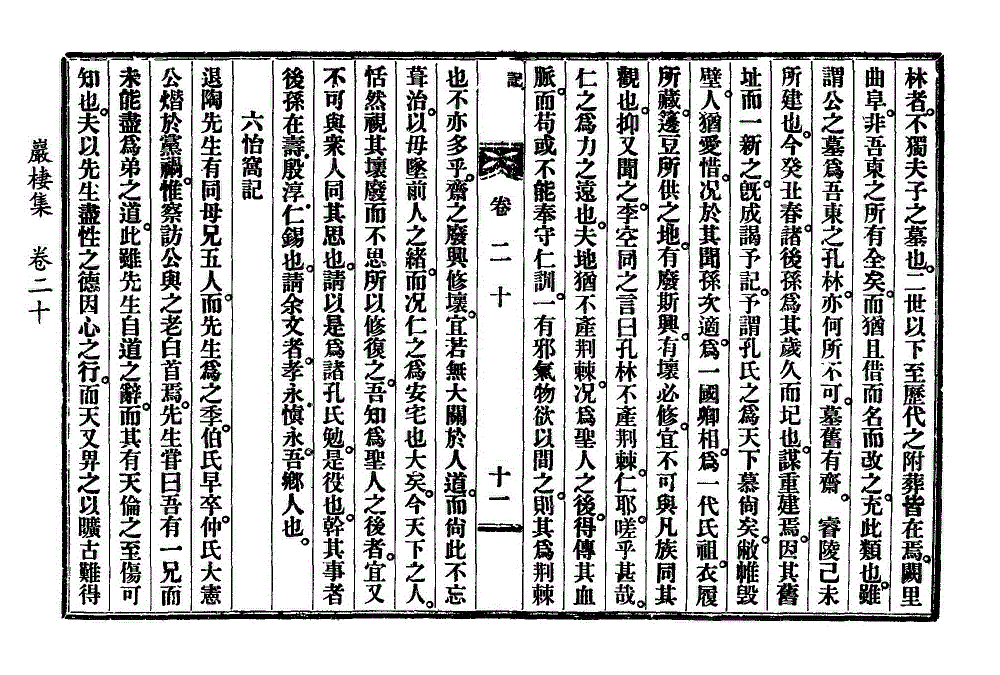 林者。不独夫子之墓也。二世以下至历代之附葬皆在焉。阙里曲阜。非吾东之所有全矣。而犹且借而名而改之。充此类也。虽谓公之墓为吾东之孔林。亦何所不可。墓旧有斋。 睿陵己未所建也。今癸丑春。诸后孙为其岁久而圮也。谋重建焉。因其旧址而一新之。既成谒予记。予谓孔氏之为天下慕尚矣。敝帷毁壁。人犹爱惜。况于其闻孙次适。为一国卿相。为一代氏祖。衣履所藏。笾豆所供之地。有废斯兴。有坏必修。宜不可与凡族同其观也。抑又闻之。李空同之言曰孔林不产荆棘。仁耶。嗟乎甚哉。仁之为力之远也。夫地犹不产荆棘。况为圣人之后。得传其血脉。而苟或不能奉守仁训。一有邪气物欲以间之。则其为荆棘也不亦多乎。斋之废兴修坏。宜若无大关于人道。而尚此不忘葺治。以毋坠前人之绪。而况仁之为安宅也大矣。今天下之人。恬然视其坏废而不思所以修复之。吾知为圣人之后者。宜又不可与众人同其思也。请以是为诸孔氏勉。是役也。干其事者后孙在寿,殷淳,仁锡也。请余文者。孝永,慎永。吾乡人也。
林者。不独夫子之墓也。二世以下至历代之附葬皆在焉。阙里曲阜。非吾东之所有全矣。而犹且借而名而改之。充此类也。虽谓公之墓为吾东之孔林。亦何所不可。墓旧有斋。 睿陵己未所建也。今癸丑春。诸后孙为其岁久而圮也。谋重建焉。因其旧址而一新之。既成谒予记。予谓孔氏之为天下慕尚矣。敝帷毁壁。人犹爱惜。况于其闻孙次适。为一国卿相。为一代氏祖。衣履所藏。笾豆所供之地。有废斯兴。有坏必修。宜不可与凡族同其观也。抑又闻之。李空同之言曰孔林不产荆棘。仁耶。嗟乎甚哉。仁之为力之远也。夫地犹不产荆棘。况为圣人之后。得传其血脉。而苟或不能奉守仁训。一有邪气物欲以间之。则其为荆棘也不亦多乎。斋之废兴修坏。宜若无大关于人道。而尚此不忘葺治。以毋坠前人之绪。而况仁之为安宅也大矣。今天下之人。恬然视其坏废而不思所以修复之。吾知为圣人之后者。宜又不可与众人同其思也。请以是为诸孔氏勉。是役也。干其事者后孙在寿,殷淳,仁锡也。请余文者。孝永,慎永。吾乡人也。六怡窝记
退陶先生有同母兄五人。而先生为之季。伯氏早卒。仲氏大宪公熸于党祸。惟察访公与之老白首焉。先生尝曰吾有一兄而未能尽为弟之道。此虽先生自道之辞。而其有天伦之至伤可知也。夫以先生尽性之德因心之行。而天又畀之以旷古难得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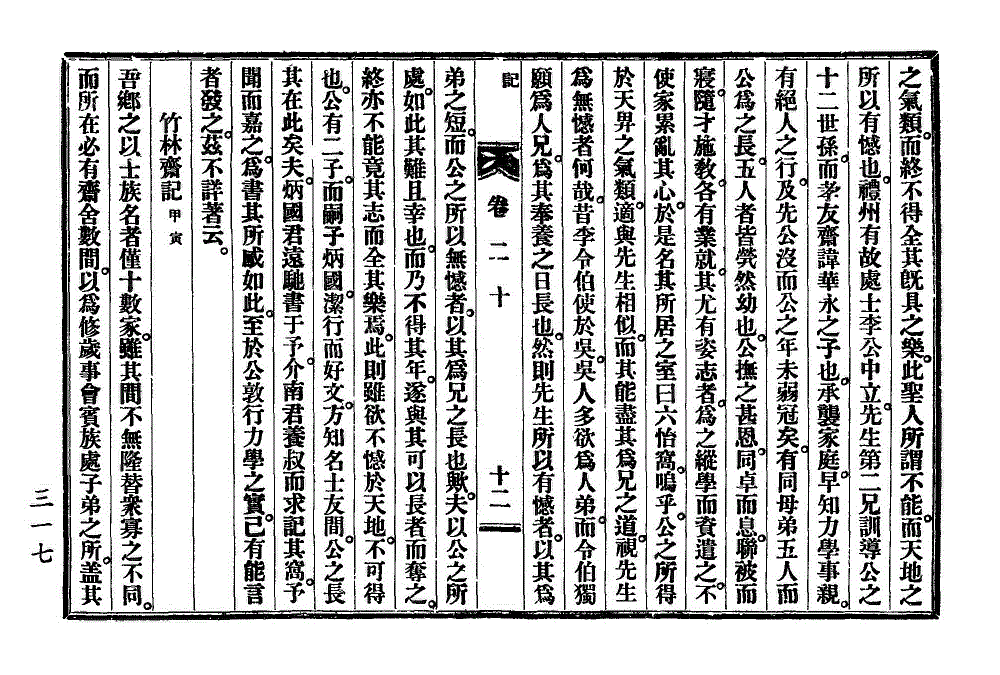 之气类。而终不得全其既具之乐。此圣人所谓不能。而天地之所以有憾也。礼州有故处士李公中立。先生第二兄训导公之十二世孙。而孝友斋讳华永之子也。承袭家庭。早知力学事亲。有绝人之行。及先公没而公之年未弱冠矣。有同母弟五人而公为之长。五人者皆茕然幼也。公抚之甚恩。同卓而息。联被而寝。随才施教。各有业就。其尤有姿志者。为之纵学而资遣之。不使家累乱其心。于是名其所居之室曰六怡窝。呜乎。公之所得于天畀之气类。适与先生相似。而其能尽其为兄之道。视先生为无憾者何哉。昔李令伯使于吴。吴人多欲为人弟。而令伯独愿为人兄。为其奉养之日长也。然则先生所以有憾者。以其为弟之短。而公之所以无憾者。以其为兄之长也欤。夫以公之所处。如此其难且幸也。而乃不得其年。遂与其可以长者而夺之。终亦不能竟其志而全其乐焉。此则虽欲不憾于天地。不可得也。公有二子。而嗣子炳国。洁行而好文。方知名士友间。公之长其在此矣夫。炳国君远驰书于予。介南君养叔而求记其窝。予闻而嘉之。为书其所感如此。至于公敦行力学之实。已有能言者发之。兹不详著云。
之气类。而终不得全其既具之乐。此圣人所谓不能。而天地之所以有憾也。礼州有故处士李公中立。先生第二兄训导公之十二世孙。而孝友斋讳华永之子也。承袭家庭。早知力学事亲。有绝人之行。及先公没而公之年未弱冠矣。有同母弟五人而公为之长。五人者皆茕然幼也。公抚之甚恩。同卓而息。联被而寝。随才施教。各有业就。其尤有姿志者。为之纵学而资遣之。不使家累乱其心。于是名其所居之室曰六怡窝。呜乎。公之所得于天畀之气类。适与先生相似。而其能尽其为兄之道。视先生为无憾者何哉。昔李令伯使于吴。吴人多欲为人弟。而令伯独愿为人兄。为其奉养之日长也。然则先生所以有憾者。以其为弟之短。而公之所以无憾者。以其为兄之长也欤。夫以公之所处。如此其难且幸也。而乃不得其年。遂与其可以长者而夺之。终亦不能竟其志而全其乐焉。此则虽欲不憾于天地。不可得也。公有二子。而嗣子炳国。洁行而好文。方知名士友间。公之长其在此矣夫。炳国君远驰书于予。介南君养叔而求记其窝。予闻而嘉之。为书其所感如此。至于公敦行力学之实。已有能言者发之。兹不详著云。竹林斋记(甲寅)
吾乡之以士族名者仅十数家。虽其间不无隆替众寡之不同。而所在必有斋舍数间。以为修岁事会宾族处子弟之所。盖其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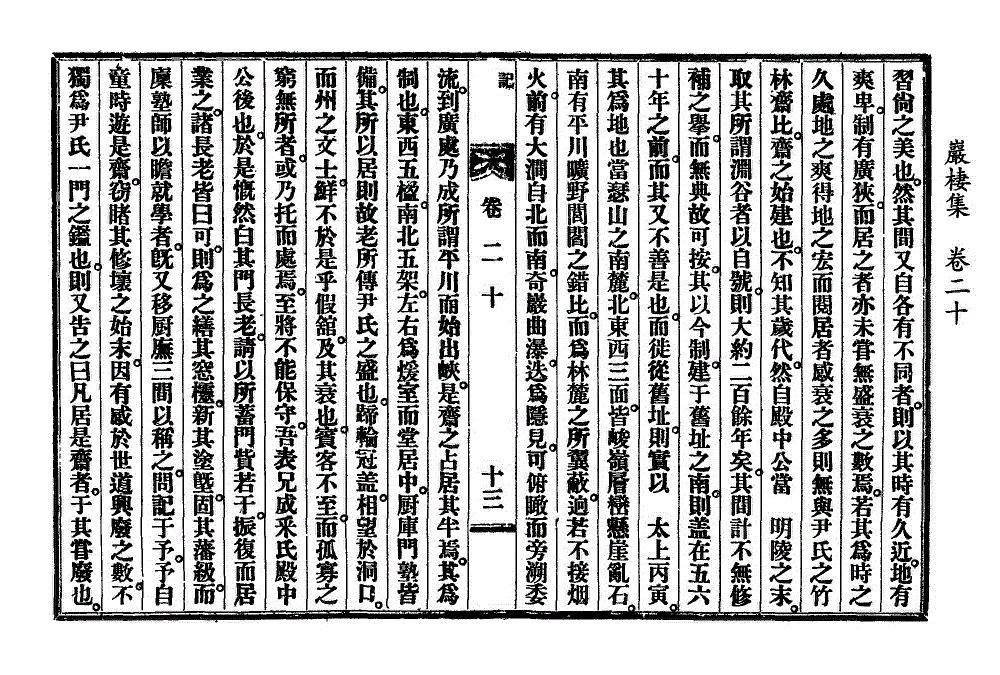 习尚之美也。然其间又自各有不同者。则以其时有久近。地有爽卑。制有广狭。而居之者亦未尝无盛衰之数焉。若其为时之久处地之爽得地之宏而阅居者感衰之多则无与尹氏之竹林斋比。斋之始建也。不知其岁代。然自殿中公当 明陵之末。取其所谓渊谷者以自号。则大约二百馀年矣。其间计不无修补之举。而无典故可按。其以今制。建于旧址之南。则盖在五六十年之前。而其又不善是也。而徙从旧址。则实以 太上丙寅。其为地也当瑟山之南麓。北东西三面。皆峻岭层峦悬崖乱石。南有平川旷野闾阎之错比。而为林麓之所翼蔽。迥若不接烟火。前有大涧自北而南。奇岩曲瀑。迭为隐见。可俯瞰而旁溯委流。到广处乃成所谓平川而始出峡。是斋之占居其半焉。其为制也。东西五楹。南北五架。左右为煖室而堂居中。厨库门塾皆备。其所以居则故老所传尹氏之盛也。蹄轮冠盖。相望于洞口。而州之文士。鲜不于是乎假馆。及其衰也。宾客不至。而孤寡之穷无所者。或乃托而处焉。至将不能保守。吾表兄成采氏殿中公后也。于是慨然白其门长老。请以所蓄门赀若干。振复而居业之。诸长老皆曰可。则为之缮其窗棂。新其涂塈。固其藩级。而廪塾师以瞻就学者。既又移厨庑三间以称之。问记于予。予自童时游是斋。窃睹其修坏之始末。因有感于世道兴废之数。不独为尹氏一门之鉴也。则又告之曰凡居是斋者。于其尝废也。
习尚之美也。然其间又自各有不同者。则以其时有久近。地有爽卑。制有广狭。而居之者亦未尝无盛衰之数焉。若其为时之久处地之爽得地之宏而阅居者感衰之多则无与尹氏之竹林斋比。斋之始建也。不知其岁代。然自殿中公当 明陵之末。取其所谓渊谷者以自号。则大约二百馀年矣。其间计不无修补之举。而无典故可按。其以今制。建于旧址之南。则盖在五六十年之前。而其又不善是也。而徙从旧址。则实以 太上丙寅。其为地也当瑟山之南麓。北东西三面。皆峻岭层峦悬崖乱石。南有平川旷野闾阎之错比。而为林麓之所翼蔽。迥若不接烟火。前有大涧自北而南。奇岩曲瀑。迭为隐见。可俯瞰而旁溯委流。到广处乃成所谓平川而始出峡。是斋之占居其半焉。其为制也。东西五楹。南北五架。左右为煖室而堂居中。厨库门塾皆备。其所以居则故老所传尹氏之盛也。蹄轮冠盖。相望于洞口。而州之文士。鲜不于是乎假馆。及其衰也。宾客不至。而孤寡之穷无所者。或乃托而处焉。至将不能保守。吾表兄成采氏殿中公后也。于是慨然白其门长老。请以所蓄门赀若干。振复而居业之。诸长老皆曰可。则为之缮其窗棂。新其涂塈。固其藩级。而廪塾师以瞻就学者。既又移厨庑三间以称之。问记于予。予自童时游是斋。窃睹其修坏之始末。因有感于世道兴废之数。不独为尹氏一门之鉴也。则又告之曰凡居是斋者。于其尝废也。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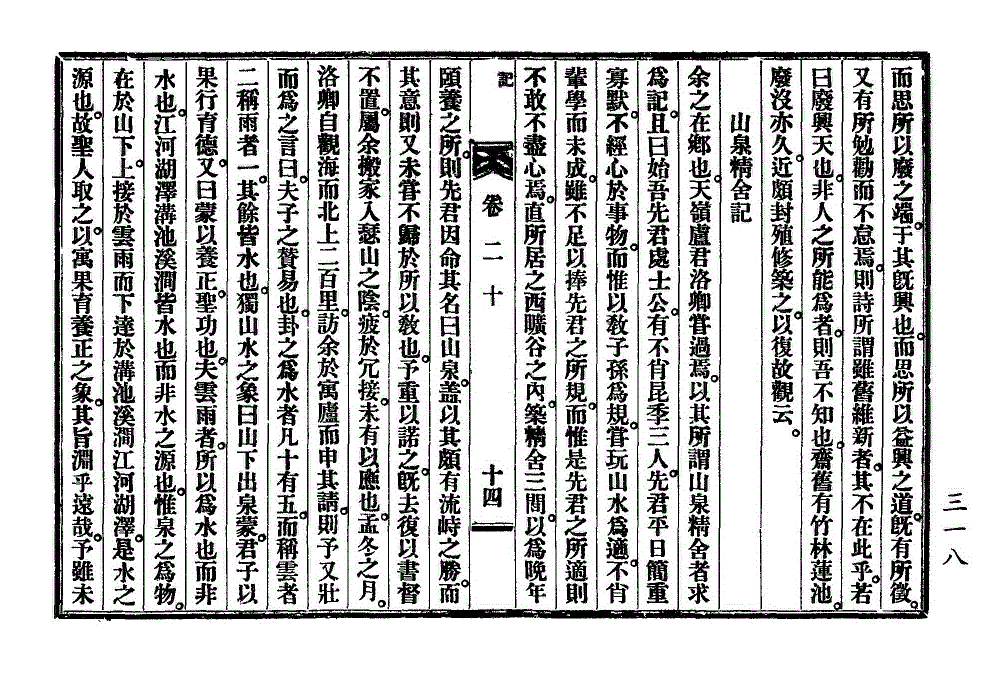 而思所以废之端。于其既兴也。而思所以益兴之道。既有所徵。又有所勉劝而不怠焉。则诗所谓虽旧维新者。其不在此乎。若曰废兴天也。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吾不知也。斋旧有竹林莲池。废没亦久。近颇封殖修筑之。以复故观云。
而思所以废之端。于其既兴也。而思所以益兴之道。既有所徵。又有所勉劝而不怠焉。则诗所谓虽旧维新者。其不在此乎。若曰废兴天也。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吾不知也。斋旧有竹林莲池。废没亦久。近颇封殖修筑之。以复故观云。山泉精舍记
余之在乡也。天岭卢君洛卿尝过焉。以其所谓山泉精舍者求为记。且曰始吾先君处士公。有不肖昆季三人。先君平日简重寡默。不经心于事物。而惟以教子孙为规。尝玩山水为适。不肖辈学而未成。虽不足以捧先君之所规。而惟是先君之所适则不敢不尽心焉。直所居之西旷谷之内。筑精舍三间。以为晚年颐养之所。则先君因命其名曰山泉。盖以其颇有流峙之胜。而其意则又未尝不归于所以教也。予重以诺之。既去复以书督不置。属余搬家入瑟山之阴。疲于冗接。未有以应也。孟冬之月。洛卿自观海而北上二百里。访余于寓庐而申其请。则予又壮而为之言曰。夫子之赞易也。卦之为水者凡十有五。而称云者二称雨者一。其馀皆水也。独山水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夫云雨者。所以为水也而非水也。江河湖泽沟池溪涧皆水也而非水之源也。惟泉之为物。在于山下。上接于云雨而下达于沟池溪涧江河湖泽。是水之源也。故圣人取之。以寓果育养正之象。其旨渊乎远哉。予虽未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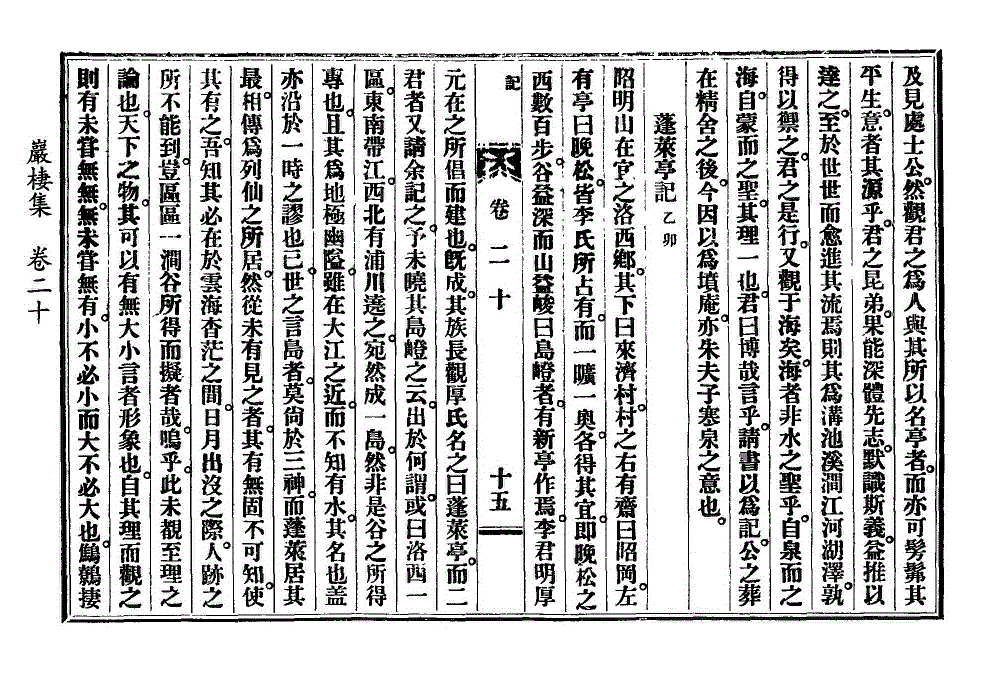 及见处士公。然观君之为人与其所以名亭者。而亦可髣髴其平生。意者其源乎。君之昆弟。果能深体先志。默识斯义。益推以达之。至于世世而愈进其流焉则其为沟池溪涧江河湖泽。孰得以御之。君之是行。又观于海矣。海者非水之圣乎。自泉而之海。自蒙而之圣。其理一也。君曰博哉言乎。请书以为记。公之葬在精舍之后。今因以为坟庵。亦朱夫子寒泉之意也。
及见处士公。然观君之为人与其所以名亭者。而亦可髣髴其平生。意者其源乎。君之昆弟。果能深体先志。默识斯义。益推以达之。至于世世而愈进其流焉则其为沟池溪涧江河湖泽。孰得以御之。君之是行。又观于海矣。海者非水之圣乎。自泉而之海。自蒙而之圣。其理一也。君曰博哉言乎。请书以为记。公之葬在精舍之后。今因以为坟庵。亦朱夫子寒泉之意也。蓬莱亭记(乙卯)
昭明山在宜之洛西乡。其下曰来济村。村之右有斋曰昭冈。左有亭曰晚松。皆李氏所占有。而一旷一奥。各得其宜。即晚松之西数百步。谷益深而山益峻曰岛嶝者。有新亭作焉。李君明厚元在之所倡而建也。既成。其族长观厚氏名之曰蓬莱亭。而二君者又请余记之。予未晓其岛嶝之云。出于何谓。或曰洛西一区。东南带江。西北有浦川绕之。宛然成一岛。然非是谷之所得专也。且其为地极幽隘。虽在大江之近。而不知有水。其名也盖亦沿于一时之谬也已。世之言岛者。莫尚于三神。而蓬莱居其最。相传为列仙之所居。然从未有见之者。其有无固不可知。使其有之。吾知其必在于云海杳茫之间。日月出没之际。人迹之所不能到。岂区区一涧谷所得而拟者哉。呜乎。此未睹至理之论也。天下之物。其可以有无大小言者形象也。自其理而观之则有未尝无无。无未尝无有。小不必小而大不必大也。鹪鹩栖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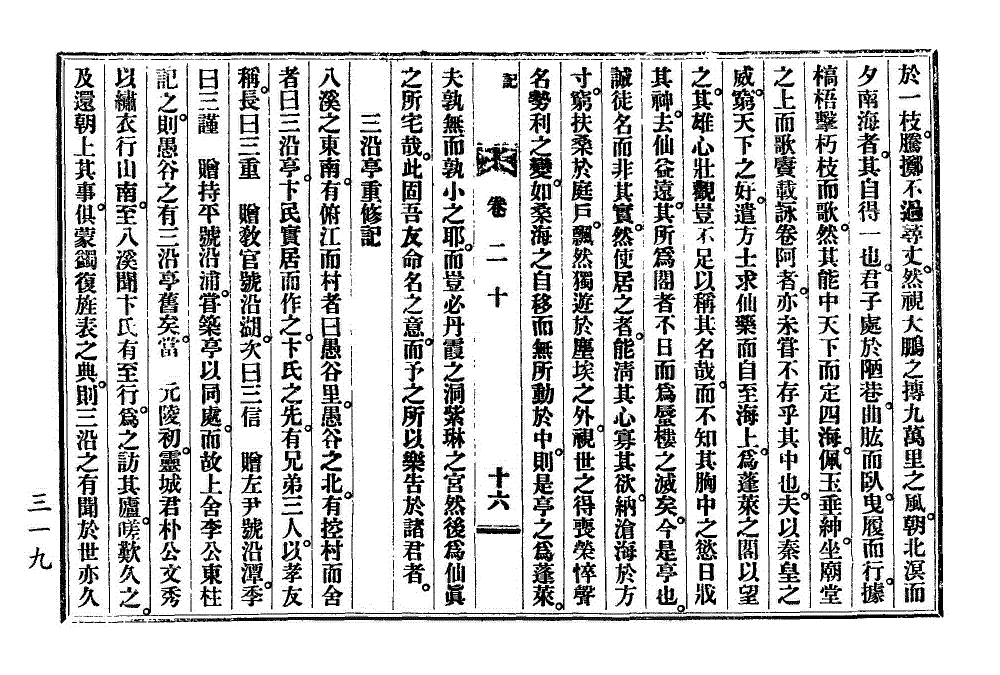 于一枝。腾掷不过寻丈。然视大鹏之抟九万里之风。朝北溟而夕南海者。其自得一也。君子处于陋巷。曲肱而卧。曳履而行。据槁梧击朽枝而歌。然其能中天下而定四海。佩玉垂绅。坐庙堂之上而歌赓载咏卷阿者。亦未尝不存乎其中也。夫以秦皇之威。穷天下之好。遣方士求仙药而自至海上。为蓬莱之阁以望之。其雄心壮观岂不足以称其名哉。而不知其胸中之欲日戕其神。去仙益远。其所为阁者不日而为蜃楼之灭矣。今是亭也。诚徒名而非其实。然使居之者。能清其心寡其欲。纳沧海于方寸。穷扶桑于庭户。飘然独游于尘埃之外。视世之得丧荣悴声名势利之变。如桑海之自移而无所动于中。则是亭之为蓬莱。夫孰无而孰小之耶。而岂必丹霞之洞紫琳之宫然后为仙真之所宅哉。此固吾友命名之意。而予之所以乐告于诸君者。
于一枝。腾掷不过寻丈。然视大鹏之抟九万里之风。朝北溟而夕南海者。其自得一也。君子处于陋巷。曲肱而卧。曳履而行。据槁梧击朽枝而歌。然其能中天下而定四海。佩玉垂绅。坐庙堂之上而歌赓载咏卷阿者。亦未尝不存乎其中也。夫以秦皇之威。穷天下之好。遣方士求仙药而自至海上。为蓬莱之阁以望之。其雄心壮观岂不足以称其名哉。而不知其胸中之欲日戕其神。去仙益远。其所为阁者不日而为蜃楼之灭矣。今是亭也。诚徒名而非其实。然使居之者。能清其心寡其欲。纳沧海于方寸。穷扶桑于庭户。飘然独游于尘埃之外。视世之得丧荣悴声名势利之变。如桑海之自移而无所动于中。则是亭之为蓬莱。夫孰无而孰小之耶。而岂必丹霞之洞紫琳之宫然后为仙真之所宅哉。此固吾友命名之意。而予之所以乐告于诸君者。三沿亭重修记
八溪之东南。有俯江而村者曰愚谷里。愚谷之北。有控村而舍者曰三沿亭。卞民实居而作之。卞氏之先。有兄弟三人。以孝友称。长曰三重 赠教官号沿湖。次曰三信 赠左尹号沿潭。季曰三谨 赠持平号沿浦。尝筑亭以同处。而故上舍李公东柱记之。则愚谷之有三沿亭旧矣。当 元陵初。灵城君朴公文秀以绣衣行山南。至八溪闻卞氏有至行。为之访其庐。嗟叹久之。及还朝上其事。俱蒙蠲复旌表之典。则三沿之有闻于世亦久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0H 页
 矣。其后百馀年而门户寝衰。生理寝薄。亭亦随而废。幸今三四十年之间。衰者日起。薄者日裕。于是向之废者复兴。既又益修而大之而属余记。余昔从诸士友屡游是里而登是亭。退而观其父兄子弟之相与。固知其有孝友之馀风矣。夫孝友之为物也。其道甚近。其效甚远。方三沿公之处于斯也。长枕大被。绝甘分少。丘垄之相望而庭户之相扶持。泯然不知其形之异也。至于今则族属日远。门户日分。利害之易以相轧而言语之易以相伤。漠然其或视之如涂人也。则是亭之作而新之。其恶可已哉。亭新而并与其道而新之。使百世之后。复睹三君子之风于一堂之上。其效岂不远哉。不然而高栋华屋。日增月饰。取以便起居而夸视听而已。则亦何益之有哉。是为记。
矣。其后百馀年而门户寝衰。生理寝薄。亭亦随而废。幸今三四十年之间。衰者日起。薄者日裕。于是向之废者复兴。既又益修而大之而属余记。余昔从诸士友屡游是里而登是亭。退而观其父兄子弟之相与。固知其有孝友之馀风矣。夫孝友之为物也。其道甚近。其效甚远。方三沿公之处于斯也。长枕大被。绝甘分少。丘垄之相望而庭户之相扶持。泯然不知其形之异也。至于今则族属日远。门户日分。利害之易以相轧而言语之易以相伤。漠然其或视之如涂人也。则是亭之作而新之。其恶可已哉。亭新而并与其道而新之。使百世之后。复睹三君子之风于一堂之上。其效岂不远哉。不然而高栋华屋。日增月饰。取以便起居而夸视听而已。则亦何益之有哉。是为记。鹤阴斋义庄记
吾族之庄于郡之西也。有鹤阴斋亦久矣。其曰义庄者。何㕫焉。自处士君讳映承为之也。始处士君籍有先人之业。颇以赀闻。而又从事于文学。盖乡人称善士矣。于是以先人之意。捐金谷若干归之斋而俾有司者殖之。凡有凶荒瘠札及门内有非泛之需。约以是应济。久之得土田若干。处士君没十年。次子柄庸摄家治。以宗赀之耗弱。请举而合之。族人秉洛以诸父兄之意。属余记其事。且曰虽无其名。记其始。以不忍没之也。嗟夫。余尝见世之为此者亦多矣。然其始也。或先名而后实。则其终也常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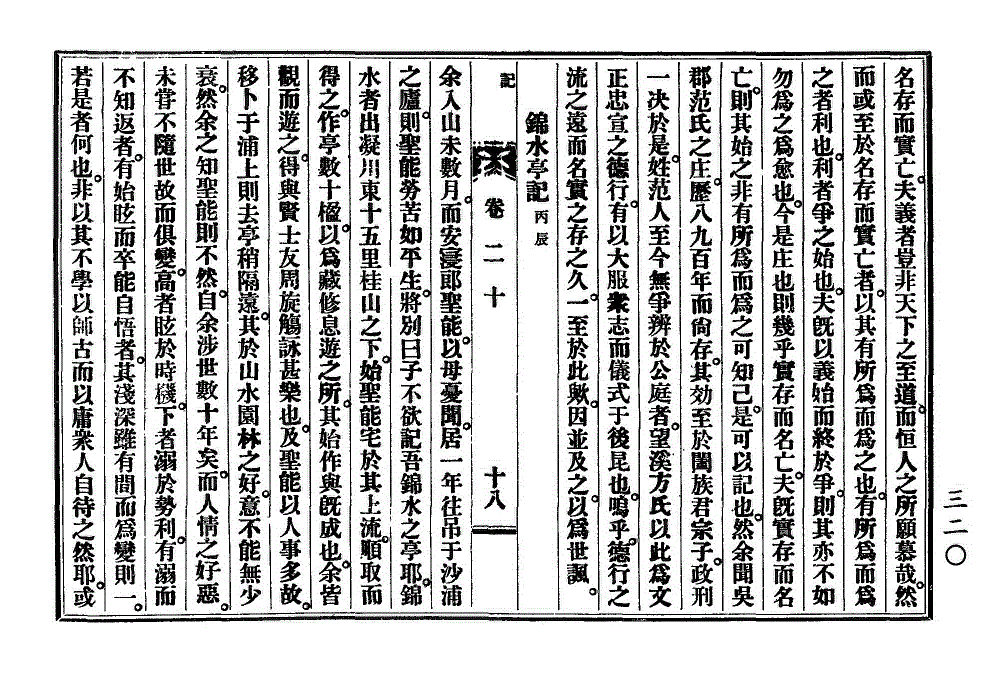 名存而实亡。夫义者岂非天下之至道。而恒人之所愿慕哉。然而或至于名存而实亡者。以其有所为而为之也。有所为而为之者利也。利者争之始也。夫既以义始而终于争。则其亦不如勿为之为愈也。今是庄也则几乎实存而名亡。夫既实存而名亡。则其始之非有所为而为之可知已。是可以记也。然余闻吴郡范氏之庄。历八九百年而尚存。其效至于阖族君宗子。政刑一决于是。姓范人至今无争辨于公庭者。望溪方氏以此为文正忠宣之德行。有以大服众志而仪式于后昆也。呜乎。德行之流之远而名实之存之久。一至于此欤。因并及之。以为世讽。
名存而实亡。夫义者岂非天下之至道。而恒人之所愿慕哉。然而或至于名存而实亡者。以其有所为而为之也。有所为而为之者利也。利者争之始也。夫既以义始而终于争。则其亦不如勿为之为愈也。今是庄也则几乎实存而名亡。夫既实存而名亡。则其始之非有所为而为之可知已。是可以记也。然余闻吴郡范氏之庄。历八九百年而尚存。其效至于阖族君宗子。政刑一决于是。姓范人至今无争辨于公庭者。望溪方氏以此为文正忠宣之德行。有以大服众志而仪式于后昆也。呜乎。德行之流之远而名实之存之久。一至于此欤。因并及之。以为世讽。锦水亭记(丙辰)
余入山未数月。而安寖郎圣能。以母忧闻。居一年往吊于沙浦之庐。则圣能劳苦如平生。将别曰子不欲记吾锦水之亭耶。锦水者出凝川东十五里桂山之下。始圣能宅于其上流。顺取而得之。作亭数十楹。以为藏修息游之所。其始作与既成也。余皆观而游之。得与贤士友周旋觞咏甚乐也。及圣能以人事多故。移卜于浦上则去亭稍隔远。其于山水园林之好。意不能无少衰。然余之知圣能则不然。自余涉世数十年矣。而人情之好恶。未尝不随世故而俱变。高者眩于时机。下者溺于势利。有溺而不知返者。有始眩而卒能自悟者。其浅深虽有间而为变则一。若是者何也。非以其不学以师古而以庸众人自待之然耶。或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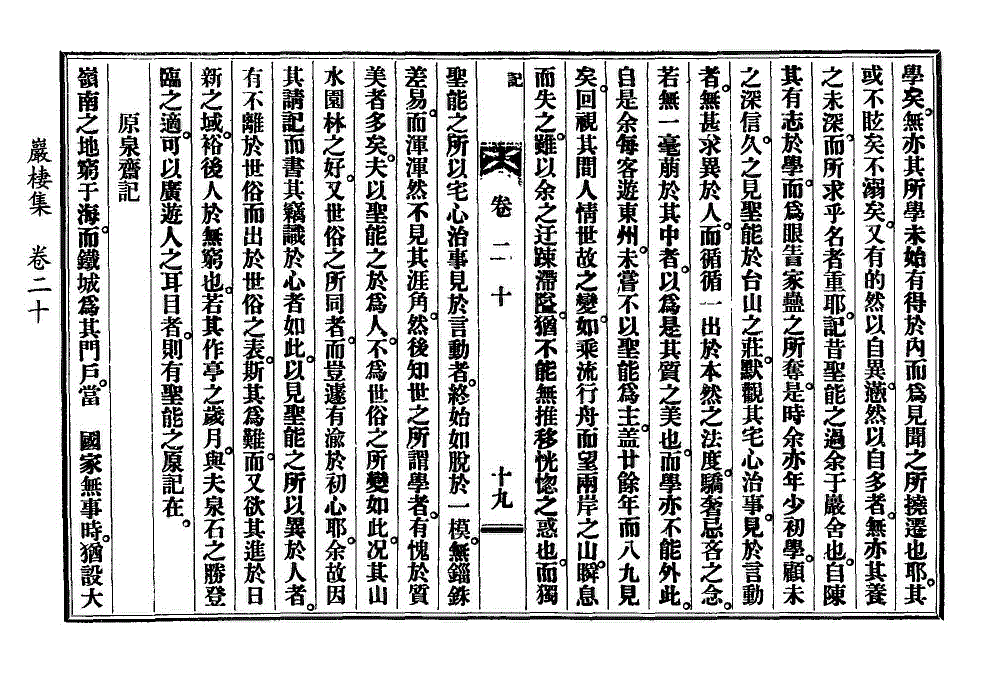 学矣。无亦其所学未始有得于内而为见闻之所挠迁也耶。其或不眩矣不溺矣。又有的然以自异。懑然以自多者。无亦其养之未深。而所求乎名者重耶。记昔圣能之过余于岩舍也。自陈其有志于学。而为眼眚家蛊之所夺。是时余亦年少初学。顾未之深信。久之见圣能于台山之庄。默观其宅心治事。见于言动者。无甚求异于人。而循循一出于本然之法度。骄奢忌吝之念。若无一毫萌于其中者。以为是其质之美也。而学亦不能外此。自是余每客游东州。未尝不以圣能为主。盖廿馀年而八九见矣。回视其间人情世故之变。如乘流行舟而望两岸之山。瞬息而失之。虽以余之迂疏滞隘。犹不能无推移恍惚之惑也。而独圣能之所以宅心治事见于言动者。终始如脱于一模。无锱铢差易。而浑浑然不见其涯角。然后知世之所谓学者。有愧于质美者多矣。夫以圣能之于为人。不为世俗之所变如此。况其山水园林之好。又世俗之所同者。而岂遽有渝于初心耶。余故因其请记而书其窃识于心者如此。以见圣能之所以异于人者。有不离于世俗而出于世俗之表。斯其为难。而又欲其进于日新之域。裕后人于无穷也。若其作亭之岁月。与夫泉石之胜登临之适。可以广游人之耳目者。则有圣能之原记在。
学矣。无亦其所学未始有得于内而为见闻之所挠迁也耶。其或不眩矣不溺矣。又有的然以自异。懑然以自多者。无亦其养之未深。而所求乎名者重耶。记昔圣能之过余于岩舍也。自陈其有志于学。而为眼眚家蛊之所夺。是时余亦年少初学。顾未之深信。久之见圣能于台山之庄。默观其宅心治事。见于言动者。无甚求异于人。而循循一出于本然之法度。骄奢忌吝之念。若无一毫萌于其中者。以为是其质之美也。而学亦不能外此。自是余每客游东州。未尝不以圣能为主。盖廿馀年而八九见矣。回视其间人情世故之变。如乘流行舟而望两岸之山。瞬息而失之。虽以余之迂疏滞隘。犹不能无推移恍惚之惑也。而独圣能之所以宅心治事见于言动者。终始如脱于一模。无锱铢差易。而浑浑然不见其涯角。然后知世之所谓学者。有愧于质美者多矣。夫以圣能之于为人。不为世俗之所变如此。况其山水园林之好。又世俗之所同者。而岂遽有渝于初心耶。余故因其请记而书其窃识于心者如此。以见圣能之所以异于人者。有不离于世俗而出于世俗之表。斯其为难。而又欲其进于日新之域。裕后人于无穷也。若其作亭之岁月。与夫泉石之胜登临之适。可以广游人之耳目者。则有圣能之原记在。原泉斋记
岭南之地穷于海。而铁城为其门户。当 国家无事时。犹设大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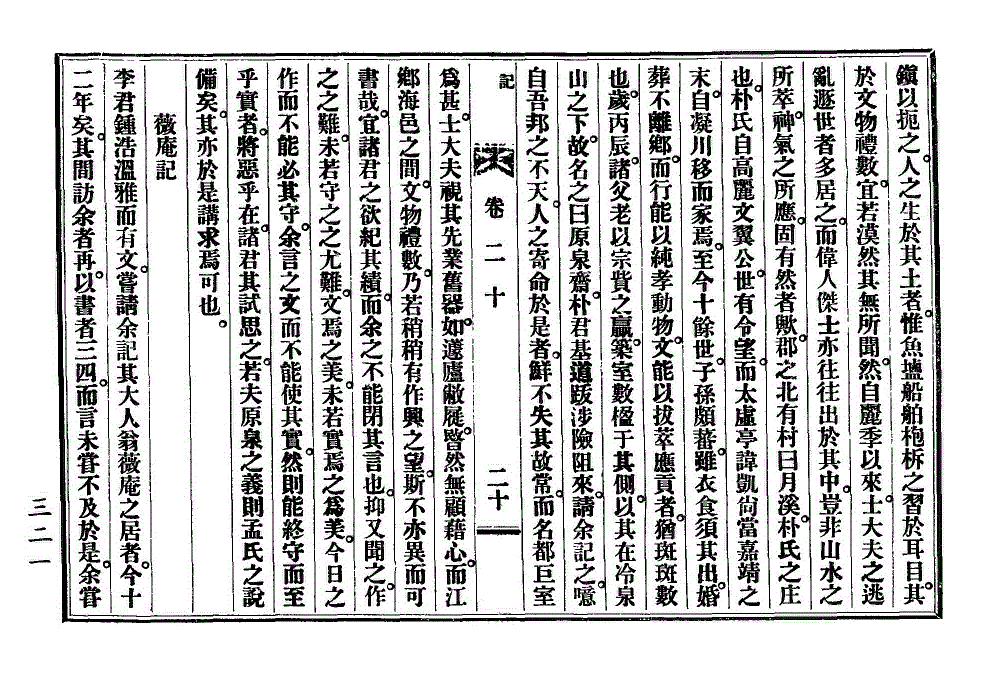 镇以扼之。人之生于其土者。惟鱼盐船舶枹柝之习于耳目。其于文物礼数。宜若漠然其无所闻。然自丽季以来。士大夫之逃乱遁世者多居之。而伟人杰士亦往往出于其中。岂非山水之所萃。神气之所应。固有然者欤。郡之北有村曰月溪。朴氏之庄也。朴氏自高丽文翼公。世有令望。而太虚亭讳凯尚当嘉靖之末。自凝川移而家焉。至今十馀世。子孙颇蕃。虽衣食须其出。婚葬不离乡。而行能以纯孝动物。文能以拔萃应贡者。犹斑斑数也。岁丙辰。诸父老以宗赀之赢。筑室数楹于其侧。以其在冷泉山之下。故名之曰原泉斋。朴君基道跋涉险阻来。请余记之。噫自吾邦之不天。人之寄命于是者。鲜不失其故常。而名都巨室为甚。士大夫视其先业旧器。如蘧庐敝屣。暋然无顾藉心。而江乡海邑之间。文物礼数。乃若稍稍有作兴之望。斯不亦异而可书哉。宜诸君之欲纪其绩。而余之不能闭其言也。抑又闻之。作之之难。未若守之之尤难。文焉之美。未若实焉之为美。今日之作而不能必其守。余言之文而不能使其实。然则能终守而至乎实者。将恶乎在。诸君其试思之。若夫原泉之义则孟氏之说备矣。其亦于是讲求焉可也。
镇以扼之。人之生于其土者。惟鱼盐船舶枹柝之习于耳目。其于文物礼数。宜若漠然其无所闻。然自丽季以来。士大夫之逃乱遁世者多居之。而伟人杰士亦往往出于其中。岂非山水之所萃。神气之所应。固有然者欤。郡之北有村曰月溪。朴氏之庄也。朴氏自高丽文翼公。世有令望。而太虚亭讳凯尚当嘉靖之末。自凝川移而家焉。至今十馀世。子孙颇蕃。虽衣食须其出。婚葬不离乡。而行能以纯孝动物。文能以拔萃应贡者。犹斑斑数也。岁丙辰。诸父老以宗赀之赢。筑室数楹于其侧。以其在冷泉山之下。故名之曰原泉斋。朴君基道跋涉险阻来。请余记之。噫自吾邦之不天。人之寄命于是者。鲜不失其故常。而名都巨室为甚。士大夫视其先业旧器。如蘧庐敝屣。暋然无顾藉心。而江乡海邑之间。文物礼数。乃若稍稍有作兴之望。斯不亦异而可书哉。宜诸君之欲纪其绩。而余之不能闭其言也。抑又闻之。作之之难。未若守之之尤难。文焉之美。未若实焉之为美。今日之作而不能必其守。余言之文而不能使其实。然则能终守而至乎实者。将恶乎在。诸君其试思之。若夫原泉之义则孟氏之说备矣。其亦于是讲求焉可也。薇庵记
李君钟浩温雅而有文。尝请余记其大人翁薇庵之居者。今十二年矣。其间访余者再。以书者三四。而言未尝不及于是。余尝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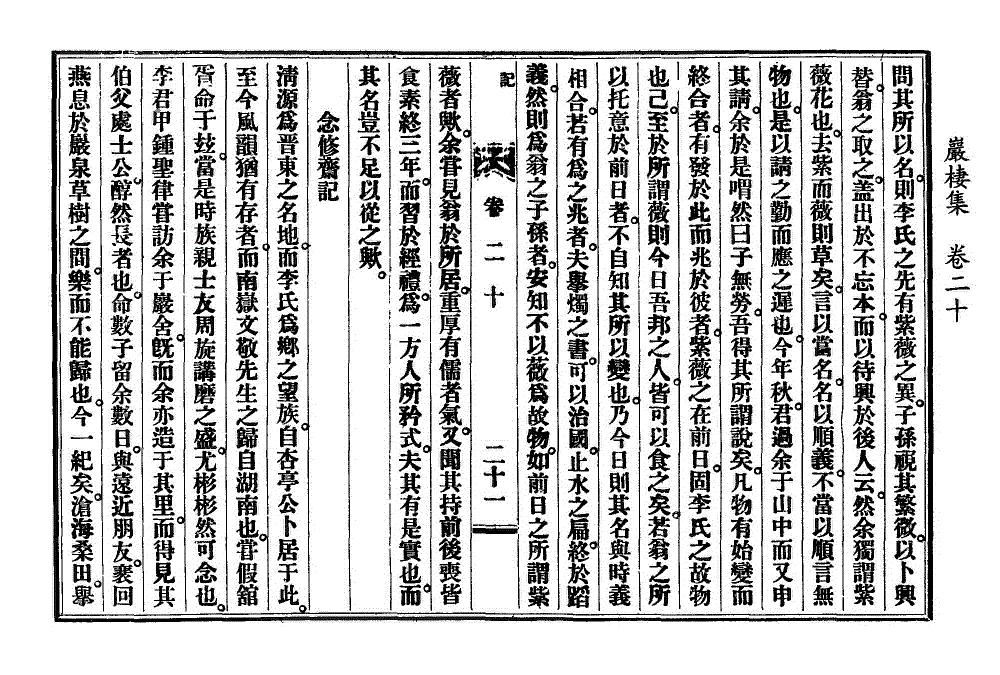 问其所以名。则李氏之先有紫薇之异。子孙视其繁微。以卜兴替。翁之取之。盖出于不忘本。而以待兴于后人云。然余独谓紫薇花也。去紫而薇则草矣。言以当名。名以顺义。不当以顺言无物也。是以请之勤而应之迟也。今年秋。君过余于山中而又申其请。余于是喟然曰子无劳。吾得其所谓说矣。凡物有始变而终合者。有发于此而兆于彼者。紫薇之在前日。固李氏之故物也已。至于所谓薇则今日吾邦之人。皆可以食之矣。若翁之所以托意于前日者。不自知其所以变也。乃今日则其名与时义相合。若有为之兆者。夫举烛之书。可以治国。止水之扁。终于蹈义。然则为翁之子孙者。安知不以薇为故物。如前日之所谓紫薇者欤。余尝见翁于所居。重厚有儒者气。又闻其持前后丧皆食素终三年。而习于经礼。为一方人所矜式。夫其有是实也。而其名岂不足以从之欤。
问其所以名。则李氏之先有紫薇之异。子孙视其繁微。以卜兴替。翁之取之。盖出于不忘本。而以待兴于后人云。然余独谓紫薇花也。去紫而薇则草矣。言以当名。名以顺义。不当以顺言无物也。是以请之勤而应之迟也。今年秋。君过余于山中而又申其请。余于是喟然曰子无劳。吾得其所谓说矣。凡物有始变而终合者。有发于此而兆于彼者。紫薇之在前日。固李氏之故物也已。至于所谓薇则今日吾邦之人。皆可以食之矣。若翁之所以托意于前日者。不自知其所以变也。乃今日则其名与时义相合。若有为之兆者。夫举烛之书。可以治国。止水之扁。终于蹈义。然则为翁之子孙者。安知不以薇为故物。如前日之所谓紫薇者欤。余尝见翁于所居。重厚有儒者气。又闻其持前后丧皆食素终三年。而习于经礼。为一方人所矜式。夫其有是实也。而其名岂不足以从之欤。念修斋记
清源为晋东之名地。而李氏为乡之望族。自杏亭公卜居于此。至今风韵犹有存者。而南岳文敬先生之归自湖南也。尝假馆胥命于玆。当是时族亲士友周旋讲磨之盛。尤彬彬然可念也。李君甲钟圣律尝访余于岩舍。既而余亦造于其里。而得见其伯父处士公。醇然长者也。命数子留余数日。与远近朋友。裴回燕息于岩泉草树之间。乐而不能归也。今一纪矣。沧海桑田。举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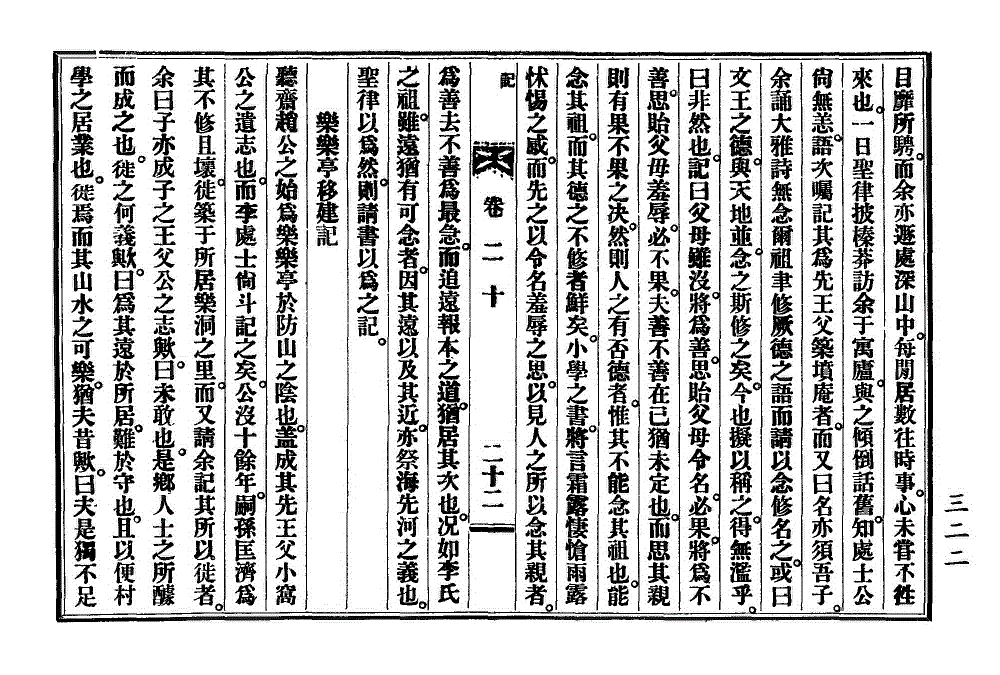 目靡所骋。而余亦遁处深山中。每閒居数往时事。心未尝不往来也。一日圣律披榛莽访余于寓庐。与之倾倒话旧。知处士公尚无恙。语次嘱记其为先王父筑坟庵者。而又曰名亦须吾子。余诵大雅诗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之语而请以念修名之。或曰文王之德。与天地并。念之斯修之矣。今也拟以称之。得无滥乎。曰非然也。记曰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夫善不善在己犹未定也。而思其亲则有果不果之决。然则人之有否德者。惟其不能念其祖也。能念其祖。而其德之不修者鲜矣。小学之书。将言霜露悽怆雨露怵惕之感。而先之以令名羞辱之思。以见人之所以念其亲者。为善去不善为最急。而追远报本之道。犹居其次也。况如李氏之祖。虽远犹有可念者。因其远以及其近。亦祭海先河之义也。圣律以为然。则请书以为之记。
目靡所骋。而余亦遁处深山中。每閒居数往时事。心未尝不往来也。一日圣律披榛莽访余于寓庐。与之倾倒话旧。知处士公尚无恙。语次嘱记其为先王父筑坟庵者。而又曰名亦须吾子。余诵大雅诗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之语而请以念修名之。或曰文王之德。与天地并。念之斯修之矣。今也拟以称之。得无滥乎。曰非然也。记曰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夫善不善在己犹未定也。而思其亲则有果不果之决。然则人之有否德者。惟其不能念其祖也。能念其祖。而其德之不修者鲜矣。小学之书。将言霜露悽怆雨露怵惕之感。而先之以令名羞辱之思。以见人之所以念其亲者。为善去不善为最急。而追远报本之道。犹居其次也。况如李氏之祖。虽远犹有可念者。因其远以及其近。亦祭海先河之义也。圣律以为然。则请书以为之记。乐乐亭移建记
听斋赵公之始为乐乐亭于防山之阴也。盖成其先王父小窝公之遗志也。而李处士尚斗记之矣。公没十馀年。嗣孙匡济为其不修且坏。徙筑于所居乐洞之里。而又请余记其所以徙者。余曰子亦成子之王父公之志欤。曰未敢也。是乡人士之所醵而成之也。徙之何义欤。曰为其远于所居。难于守也。且以便村学之居业也。徙焉而其山水之可乐。犹夫昔欤。曰夫是独不足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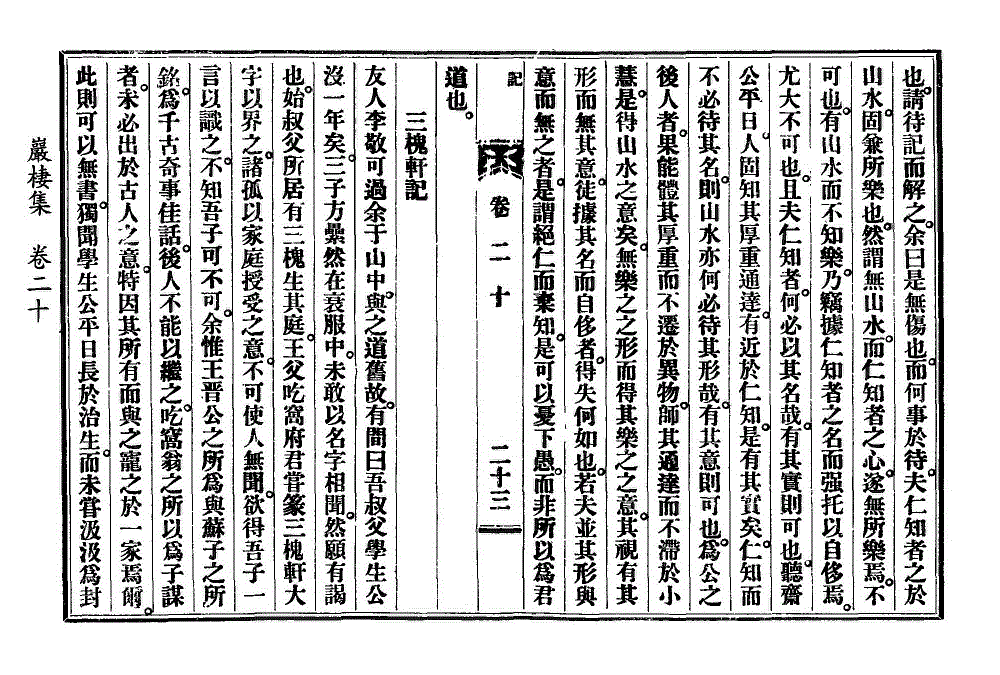 也。请待记而解之。余曰是无伤也。而何事于待。夫仁知者之于山水。固兼所乐也。然谓无山水。而仁知者之心。遂无所乐焉。不可也。有山水而不知乐。乃窃据仁知者之名而强托以自侈焉。尤大不可也。且夫仁知者。何必以其名哉。有其实则可也。听斋公平日。人固知其厚重通达。有近于仁知。是有其实矣。仁知而不必待其名。则山水亦何必待其形哉。有其意则可也。为公之后人者。果能体其厚重而不迁于异物。师其通达而不滞于小慧。是得山水之意矣。无乐之之形而得其乐之之意。其视有其形而无其意。徒据其名而自侈者。得失何如也。若夫并其形与意而无之者。是谓绝仁而弃知。是可以忧下愚。而非所以为君道也。
也。请待记而解之。余曰是无伤也。而何事于待。夫仁知者之于山水。固兼所乐也。然谓无山水。而仁知者之心。遂无所乐焉。不可也。有山水而不知乐。乃窃据仁知者之名而强托以自侈焉。尤大不可也。且夫仁知者。何必以其名哉。有其实则可也。听斋公平日。人固知其厚重通达。有近于仁知。是有其实矣。仁知而不必待其名。则山水亦何必待其形哉。有其意则可也。为公之后人者。果能体其厚重而不迁于异物。师其通达而不滞于小慧。是得山水之意矣。无乐之之形而得其乐之之意。其视有其形而无其意。徒据其名而自侈者。得失何如也。若夫并其形与意而无之者。是谓绝仁而弃知。是可以忧下愚。而非所以为君道也。三槐轩记
友人李敬可过余于山中。与之道旧故。有间曰吾叔父学生公没一年矣。三子方累然在衰服中。未敢以名字相闻。然愿有谒也。始叔父所居有三槐生其庭。王父吃窝府君尝篆三槐轩大字以界之。诸孤以家庭授受之意。不可使人无闻。欲得吾子一言以识之。不知吾子可不可。余惟王晋公之所为与苏子之所铭。为千古奇事佳话。后人不能以继之。吃窝翁之所以为子谋者。未必出于古人之意。特因其所有而与之宠之于一家焉尔。此则可以无书。独闻学生公平日长于治生。而未尝汲汲为封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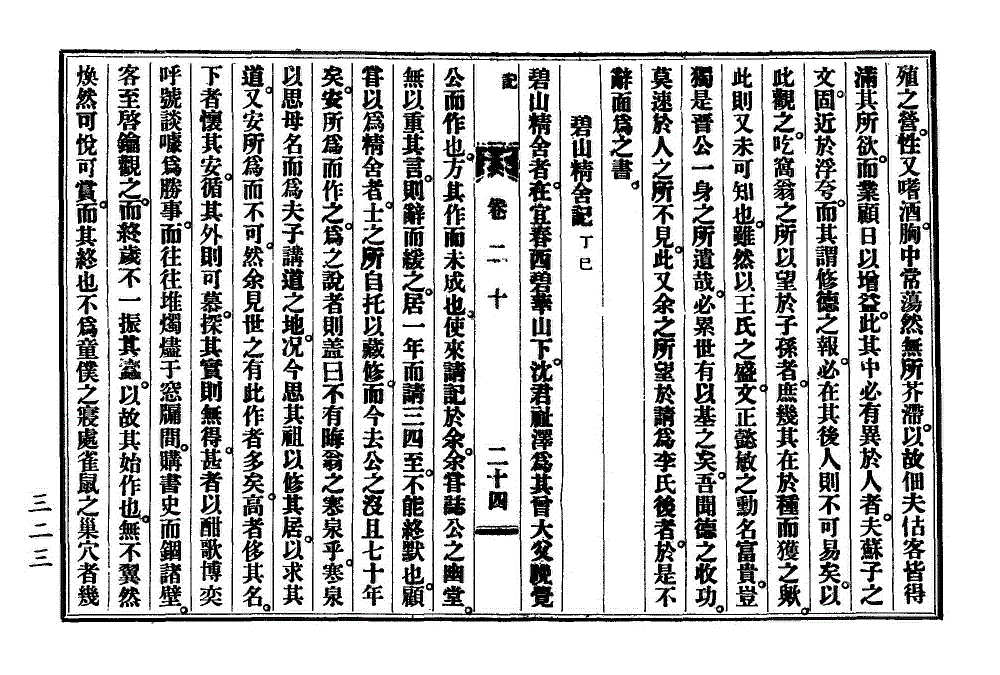 殖之营。性又嗜酒。胸中常荡然无所芥滞。以故佃夫估客皆得满其所欲。而业顾日以增益。此其中必有异于人者。夫苏子之文。固近于浮夸。而其谓修德之报。必在其后人则不可易矣。以此观之。吃窝翁之所以望于子孙者。庶几其在于种而获之欤。此则又未可知也。虽然以王氏之盛。文正懿敏之勋名富贵。岂独是晋公一身之所遗哉。必累世有以基之矣。吾闻德之收功。莫速于人之所不见。此又余之所望于请为李氏后者。于是不辞而为之书。
殖之营。性又嗜酒。胸中常荡然无所芥滞。以故佃夫估客皆得满其所欲。而业顾日以增益。此其中必有异于人者。夫苏子之文。固近于浮夸。而其谓修德之报。必在其后人则不可易矣。以此观之。吃窝翁之所以望于子孙者。庶几其在于种而获之欤。此则又未可知也。虽然以王氏之盛。文正懿敏之勋名富贵。岂独是晋公一身之所遗哉。必累世有以基之矣。吾闻德之收功。莫速于人之所不见。此又余之所望于请为李氏后者。于是不辞而为之书。碧山精舍记(丁巳)
碧山精舍者。在宜春西碧华山下。沈君祉泽为其曾大父晚觉公而作也。方其作而未成也。使来请记于余。余尝志公之幽堂。无以重其言。则辞而缓之。居一年而请三四至。不能终默也。顾尝以为精舍者。士之所自托以藏修。而今去公之没且七十年矣。安所为而作之。为之说者则盖曰不有晦翁之寒泉乎。寒泉以思母名而为夫子讲道之地。况今思其祖以修其居。以求其道。又安所为而不可。然余见世之有此作者多矣。高者侈其名。下者怀其安。循其外则可慕。探其实则无得。甚者以酣歌博奕呼号谈噱为胜事。而往往堆烛烬于窗牖间。购书史而锢诸壁。客至启钥观之。而终岁不一振其蠹。以故其始作也。无不翼然焕然可悦可赏。而其终也不为童仆之寝处雀鼠之巢穴者几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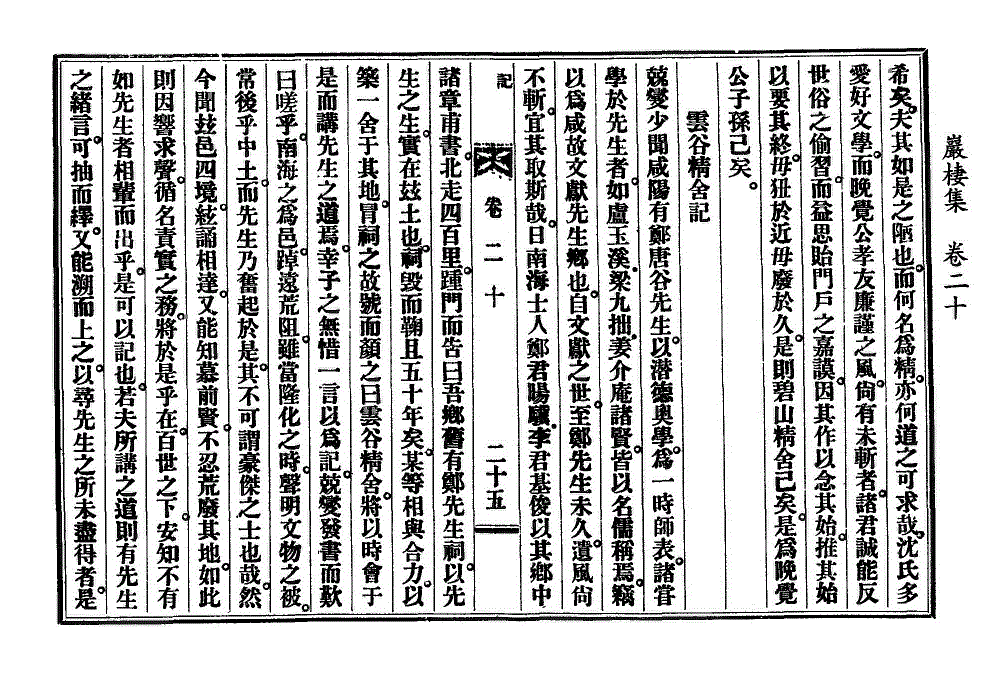 希矣。夫其如是之陋也。而何名为精。亦何道之可求哉。沈氏多爱好文学。而晚觉公孝友廉谨之风。尚有未斩者。诸君诚能反世俗之偷习。而益思贻门户之嘉谟。因其作以念其始。推其始以要其终。毋狃于近毋废于久。是则碧山精舍已矣。是为晚觉公子孙已矣。
希矣。夫其如是之陋也。而何名为精。亦何道之可求哉。沈氏多爱好文学。而晚觉公孝友廉谨之风。尚有未斩者。诸君诚能反世俗之偷习。而益思贻门户之嘉谟。因其作以念其始。推其始以要其终。毋狃于近毋废于久。是则碧山精舍已矣。是为晚觉公子孙已矣。云谷精舍记
兢燮少闻咸阳有郑唐谷先生。以潜德奥学。为一时师表。诸尝学于先生者。如卢玉溪,梁九拙,姜介庵诸贤。皆以名儒称焉。窃以为咸故文献先生乡也。自文献之世。至郑先生未久。遗风尚不斩。宜其取斯哉。日南海士人郑君旸骥,李君基俊以其乡中诸章甫书。北走四百里。踵门而告曰吾乡旧有郑先生祠。以先生之生。实在玆土也。祠毁而鞠且五十年矣。某等相与合力。以筑一舍于其地。冒祠之故号而颜之曰云谷精舍。将以时会于是而讲先生之道焉。幸子之无惜一言以为记。兢燮发书而叹曰嗟乎。南海之为邑。踔远荒阻。虽当隆化之时。声明文物之被。常后乎中土。而先生乃奋起于是。其不可谓豪杰之士也哉。然今闻玆邑四境。弦诵相达。又能知慕前贤。不忍荒废其地。如此则因响求声。循名责实之务。将于是乎在。百世之下。安知不有如先生者相辈而出乎。是可以记也。若夫所讲之道则有先生之绪言。可抽而绎。又能溯而上之。以寻先生之所未尽得者。是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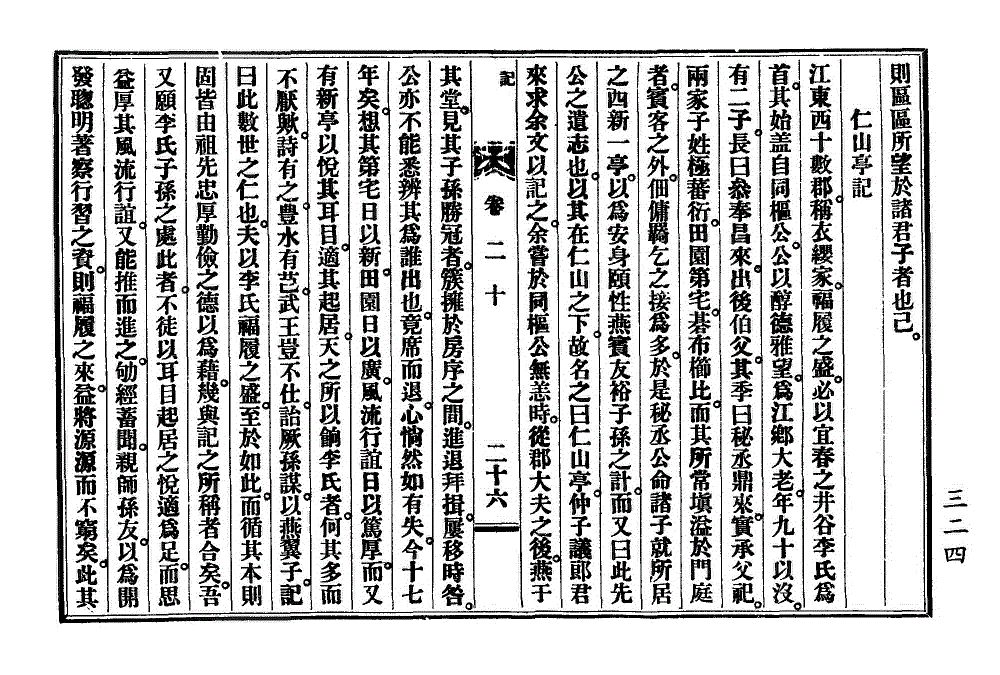 则区区所望于诸君子者也已。
则区区所望于诸君子者也已。仁山亭记
江东西十数郡。称衣缨家。福履之盛。必以宜春之井谷李氏为首。其始盖自同枢公。公以醇德雅望。为江乡大老。年九十以没。有二子。长曰参奉昌来。出后伯父。其季曰秘丞鼎来。实承父祀。两家子姓极蕃衍。田园第宅。棋布栉比。而其所常填溢于门庭者。宾客之外。佃佣羁乞之接为多。于是秘丞公命诸子就所居之西新一亭。以为安身颐性燕宾友裕子孙之计。而又曰此先公之遗志也。以其在仁山之下。故名之曰仁山亭。仲子议郎君来求余文以记之。余尝于同枢公无恙时。从郡大夫之后。燕于其堂。见其子孙胜冠者。簇拥于房序之间。进退拜揖。屡移时咎。公亦不能悉辨其为谁出也。竟席而退。心惝然如有失。今十七年矣。想其第宅日以新。田园日以广。风流行谊日以笃厚。而又有新亭以悦其耳目。适其起居。天之所以饷李氏者。何其多而不厌欤。诗有之。礼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记曰此数世之仁也。夫以李氏福履之盛。至于如此。而循其本则固皆由祖先忠厚勤俭之德以为藉。几与记之所称者合矣。吾又愿李氏子孙之处此者。不徒以耳目起居之悦适为足。而思益厚其风流行谊。又能推而进之。劬经蓄闻。亲师孙友。以为开发聪明著察行习之资。则福履之来。益将源源而不穷矣。此其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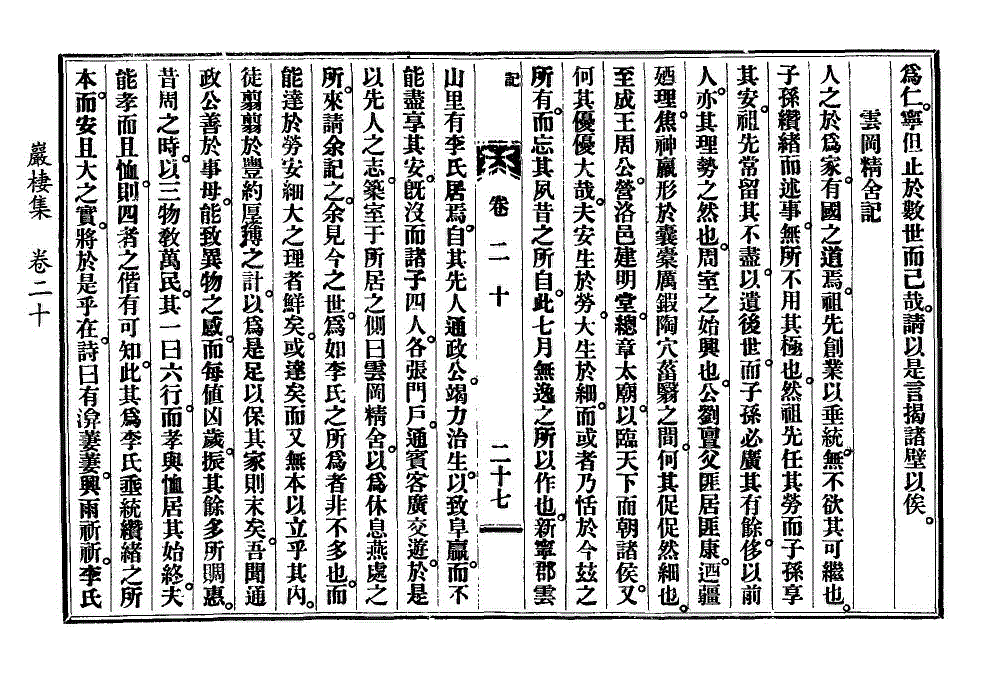 为仁。宁但止于数世而已哉。请以是言揭诸壁以俟。
为仁。宁但止于数世而已哉。请以是言揭诸壁以俟。云冈精舍记
人之于为家。有国之道焉。祖先创业以垂统。无不欲其可继也。子孙缵绪而述事。无所不用其极也。然祖先任其劳而子孙享其安。祖先常留其不尽。以遗后世。而子孙必广其有馀。侈以前人。亦其理势之然也。周室之始兴也。公刘亶父匪居匪康。乃疆乃理。焦神羸形于囊橐厉锻陶穴菑翳之间。何其促促然细也。至成王周公。营洛邑建明堂。总章太庙。以临天下而朝诸侯。又何其优优大哉。夫安生于劳。大生于细。而或者乃恬于今玆之所有。而忘其夙昔之所自。此七月无逸之所以作也。新宁郡云山里有李氏居焉。自其先人通政公。竭力治生。以致阜赢。而不能尽享其安。既没而诸子四人。各张门户。通宾客广交游。于是以先人之志。筑室于所居之侧曰云冈精舍。以为休息燕处之所。来请余记之。余见今之世。为如李氏之所为者非不多也。而能达于劳安细大之理者鲜矣。或达矣而又无本以立乎其内。徒剪剪于丰约厚薄之计。以为是足以保其家则末矣。吾闻通政公善于事母。能致异物之感。而每值凶岁。振其馀多所赒惠。昔周之时。以三物教万民。其一曰六行。而孝与恤居其始终。夫能孝而且恤。则四者之偕有可知。此其为李氏垂统缵绪之所本。而安且大之实。将于是乎在。诗曰有渰萋萋。兴雨祈祈。李氏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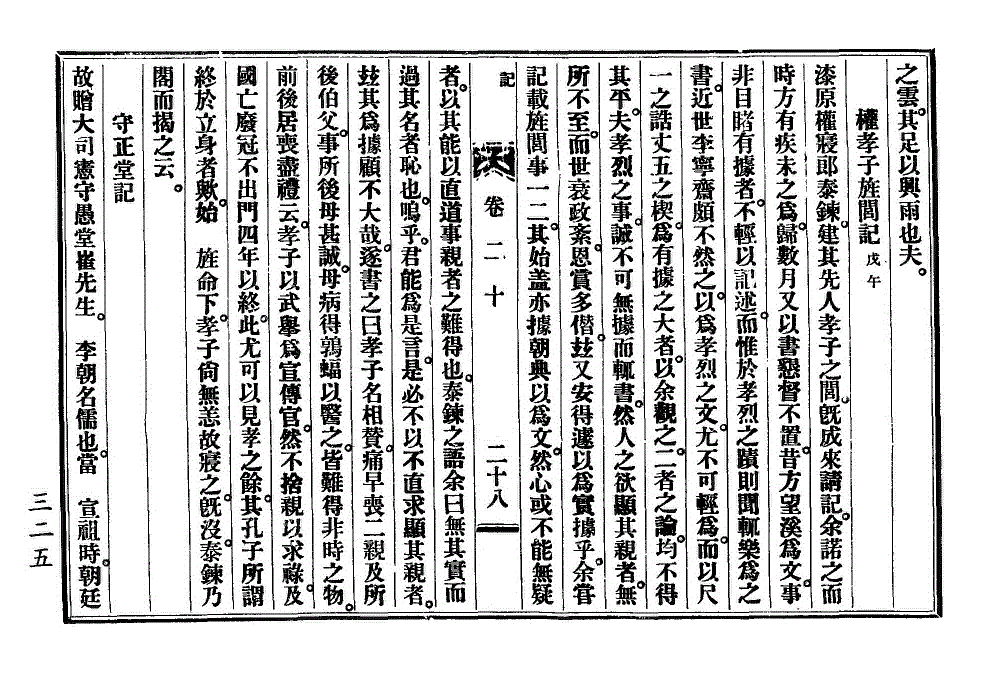 之云。其足以兴雨也夫。
之云。其足以兴雨也夫。权孝子旌闾记(戊午)
漆原权寝郎泰鍊。建其先人孝子之闾。既成来请记。余诺之而时方有疾未之为。归数月又以书恳督不置。昔方望溪为文。事非目睹有据者。不轻以记述。而惟于孝烈之迹则闻辄乐为之书。近世李宁斋颇不然之。以为孝烈之文。尤不可轻为。而以尺一之诰丈五之楔。为有据之大者。以余观之。二者之论。均不得其平。夫孝烈之事。诚不可无据而辄书。然人之欲显其亲者。无所不至。而世衰政紊。恩赏多僭。玆又安得遽以为实据乎。余尝记载旌闾事一二。其始盖亦据朝典以为文。然心或不能无疑者。以其能以直道事亲者之难得也。泰鍊之语余曰无其实而过其名者耻也。呜乎。君能为是言。是必不以不直求显其亲者。玆其为据顾不大哉。遂书之曰孝子名相赞。痛早丧二亲及所后伯父。事所后母甚诚。母病得鹑蝠以医之。皆难得非时之物。前后居丧尽礼云。孝子以武举为宣传官。然不舍亲以求禄。及国亡废冠不出门四年以终。此尤可以见孝之馀。其孔子所谓终于立身者欤。始 旌命下。孝子尚无恙故寝之。既没。泰鍊乃阁而揭之云。
守正堂记
故赠大司宪守愚堂崔先生。 李朝名儒也。当 宣祖时。朝廷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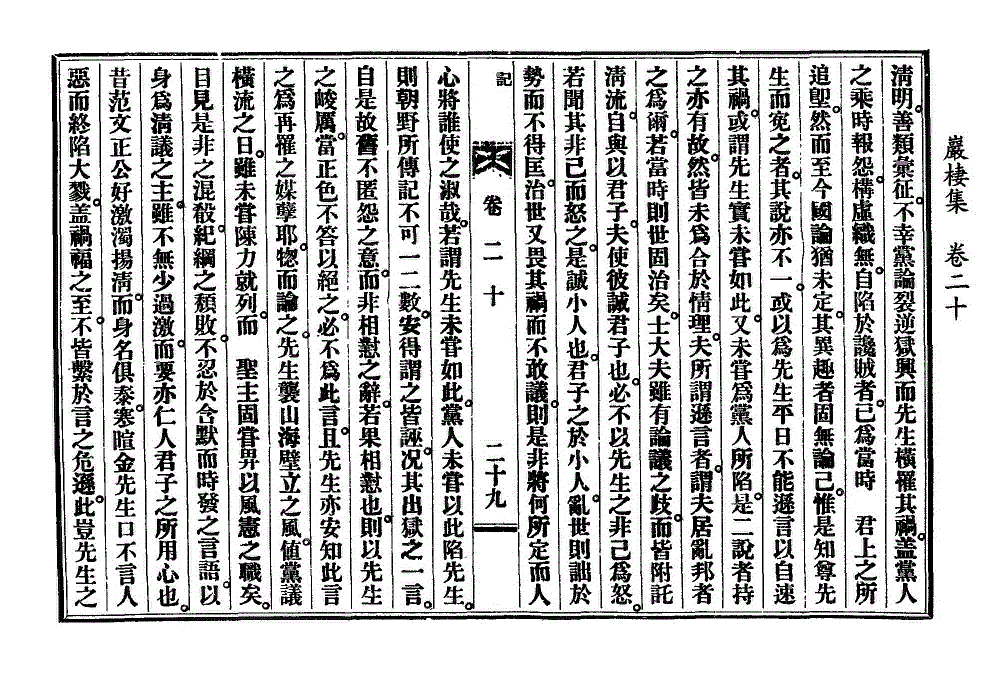 清明。善类汇征。不幸党论裂逆狱兴而先生横罹其祸。盖党人之乘时报怨。构虚织无。自陷于谗贼者。已为当时 君上之所追堲。然而至今国论犹未定。其异趣者固无论已。惟是知尊先生而冤之者。其说亦不一。或以为先生平日不能逊言以自速其祸。或谓先生实未尝如此。又未尝为党人所陷。是二说者持之亦有故。然皆未为合于情理。夫所谓逊言者。谓夫居乱邦者之为尔。若当时则世固治矣。士大夫虽有论议之歧。而皆附托清流。自与以君子。夫使彼诚君子也。必不以先生之非己为怒。若闻其非己而怒之。是诚小人也。君子之于小人。乱世则诎于势而不得匡。治世又畏其祸而不敢议。则是非将何所定而人心将谁使之淑哉。若谓先生未尝如此。党人未尝以此陷先生。则朝野所传记不可一二数。安得谓之皆诬。况其出狱之一言。自是故旧不匿怨之意。而非相怼之辞。若果相怼也。则以先生之峻厉。当正色不答以绝之。必不为此言。且先生亦安知此言之为再罹之媒孽耶。揔而论之。先生袭山海壁立之风。值党议横流之日。虽未尝陈力就列。而 圣主固尝畀以风宪之职矣。目见是非之混殽。纪纲之颓败。不忍于含默而时发之言语。以身为清议之主。虽不无少过激。而要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昔范文正公好激浊扬清。而身名俱泰。寒暄金先生口不言人恶而终陷大戮。盖祸福之至。不皆系于言之危逊。此岂先生之
清明。善类汇征。不幸党论裂逆狱兴而先生横罹其祸。盖党人之乘时报怨。构虚织无。自陷于谗贼者。已为当时 君上之所追堲。然而至今国论犹未定。其异趣者固无论已。惟是知尊先生而冤之者。其说亦不一。或以为先生平日不能逊言以自速其祸。或谓先生实未尝如此。又未尝为党人所陷。是二说者持之亦有故。然皆未为合于情理。夫所谓逊言者。谓夫居乱邦者之为尔。若当时则世固治矣。士大夫虽有论议之歧。而皆附托清流。自与以君子。夫使彼诚君子也。必不以先生之非己为怒。若闻其非己而怒之。是诚小人也。君子之于小人。乱世则诎于势而不得匡。治世又畏其祸而不敢议。则是非将何所定而人心将谁使之淑哉。若谓先生未尝如此。党人未尝以此陷先生。则朝野所传记不可一二数。安得谓之皆诬。况其出狱之一言。自是故旧不匿怨之意。而非相怼之辞。若果相怼也。则以先生之峻厉。当正色不答以绝之。必不为此言。且先生亦安知此言之为再罹之媒孽耶。揔而论之。先生袭山海壁立之风。值党议横流之日。虽未尝陈力就列。而 圣主固尝畀以风宪之职矣。目见是非之混殽。纪纲之颓败。不忍于含默而时发之言语。以身为清议之主。虽不无少过激。而要亦仁人君子之所用心也。昔范文正公好激浊扬清。而身名俱泰。寒暄金先生口不言人恶而终陷大戮。盖祸福之至。不皆系于言之危逊。此岂先生之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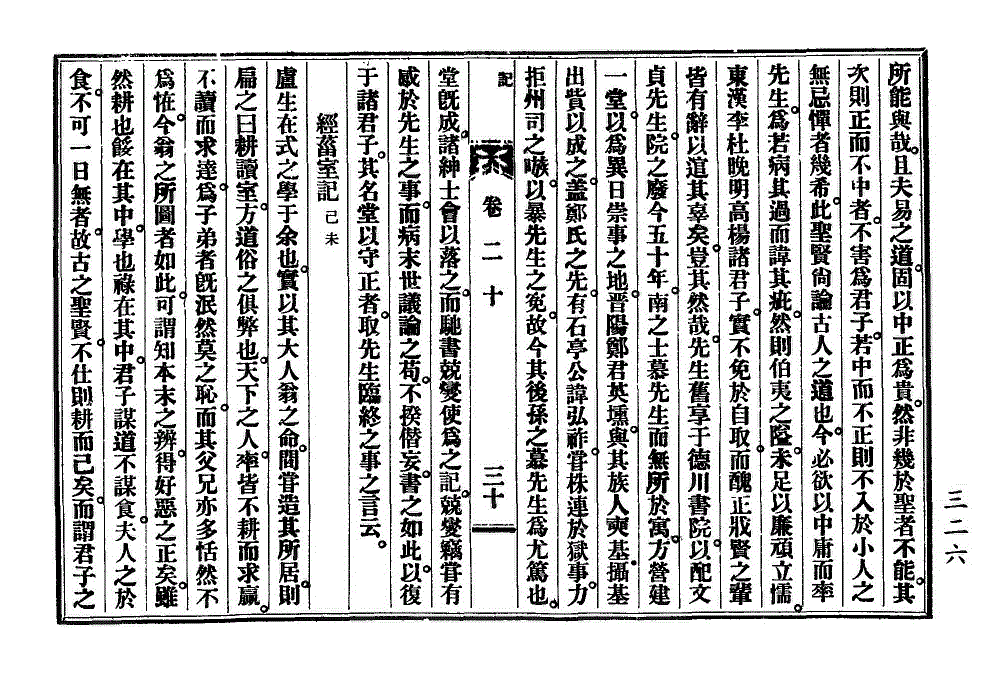 所能与哉。且夫易之道。固以中正为贵。然非几于圣者不能。其次则正而不中者。不害为君子。若中而不正则不入于小人之无忌惮者几希。此圣贤尚论古人之道也。今必欲以中庸而率先生。为若病其过而讳其疵。然则伯夷之隘。未足以廉顽立懦。东汉李杜晚明高杨诸君子。实不免于自取。而丑正戕贤之辈皆有辞以逭其辜矣。岂其然哉。先生旧享于德川书院。以配文贞先生。院之废今五十年。南之士慕先生而无所于寓。方营建一堂。以为异日崇事之地。晋阳郑君英埙。与其族人奭基,摄基出赀以成之。盖郑氏之先。有石亭公讳弘祚。尝株连于狱事。力拒州司之嗾。以暴先生之冤。故今其后孙之慕先生为尤笃也。堂既成。诸绅士会以落之。而驰书兢燮使为之记。兢燮窃尝有感于先生之事。而病末世议论之苟。不揆僭妄。书之如此。以复于诸君子。其名堂以守正者。取先生临终之事之言云。
所能与哉。且夫易之道。固以中正为贵。然非几于圣者不能。其次则正而不中者。不害为君子。若中而不正则不入于小人之无忌惮者几希。此圣贤尚论古人之道也。今必欲以中庸而率先生。为若病其过而讳其疵。然则伯夷之隘。未足以廉顽立懦。东汉李杜晚明高杨诸君子。实不免于自取。而丑正戕贤之辈皆有辞以逭其辜矣。岂其然哉。先生旧享于德川书院。以配文贞先生。院之废今五十年。南之士慕先生而无所于寓。方营建一堂。以为异日崇事之地。晋阳郑君英埙。与其族人奭基,摄基出赀以成之。盖郑氏之先。有石亭公讳弘祚。尝株连于狱事。力拒州司之嗾。以暴先生之冤。故今其后孙之慕先生为尤笃也。堂既成。诸绅士会以落之。而驰书兢燮使为之记。兢燮窃尝有感于先生之事。而病末世议论之苟。不揆僭妄。书之如此。以复于诸君子。其名堂以守正者。取先生临终之事之言云。经菑室记(己未)
卢生在式之学于余也。实以其大人翁之命。间尝造其所居。则扁之曰耕读室。方道俗之俱弊也。天下之人。率皆不耕而求赢。不读而求达。为子弟者既泯然莫之耻。而其父兄亦多恬然不为怪。今翁之所图者如此。可谓知本末之辨。得好恶之正矣。虽然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谋道不谋食。夫人之于食。不可一日无者。故古之圣贤。不仕则耕而已矣。而谓君子之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7H 页
 不谋食。其意可知也。则耕固不可与读偶也明矣。而况欲先彼而后此乎。且耕之事于野。读之事于室。今于读者所有事之室而以事乎野者混之。亦似不中于理。于是请以经菑易之。翁遂不以为不可。既而徵一言而记其说。余惟古之时。能读者必得其食。及世之浇也。则独耕者可以力食。不耕不读者。或能以智诈食。而惟读者最受其病。夫焉知经训之为菑畬哉。抑孟子曰饱乎仁义。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夫能读而至于仁义以饱其身。则虽有千顷之田万钟之禄。不屑易也。而况有时乎兼得欤。翁务本乐善。所以塈壅其后人者既优矣。生乎其益思其所以种穫哉。
不谋食。其意可知也。则耕固不可与读偶也明矣。而况欲先彼而后此乎。且耕之事于野。读之事于室。今于读者所有事之室而以事乎野者混之。亦似不中于理。于是请以经菑易之。翁遂不以为不可。既而徵一言而记其说。余惟古之时。能读者必得其食。及世之浇也。则独耕者可以力食。不耕不读者。或能以智诈食。而惟读者最受其病。夫焉知经训之为菑畬哉。抑孟子曰饱乎仁义。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夫能读而至于仁义以饱其身。则虽有千顷之田万钟之禄。不屑易也。而况有时乎兼得欤。翁务本乐善。所以塈壅其后人者既优矣。生乎其益思其所以种穫哉。春在堂记
吾乡族姓之阀。仅十数家。而吾族居其一。吾族之宅于一坊者为里三四。而梅山氏居其一。乡俗好营斋舍。以为奉先合族待宾授徒之所。一境之内。至百馀区。以盛替为多少。以赡约为侈陋。而其成否则系乎能拙焉。梅山氏其丽及赀。在盛替赡约之间。而得成五楹之宫于所居之左。卒免于陋而疑于侈。则以其能也。既成请兢燮名而记之。余用昔人诗语名之曰春在堂。而至记则方自立禁约。难于毁之。然念此自一家事。又记七八岁时先人游京师。无所于学。挟册就师于是里。当是时有草屋二间在于今所筑处。每于风檐土床间。开卷咿唔。间则从辈流走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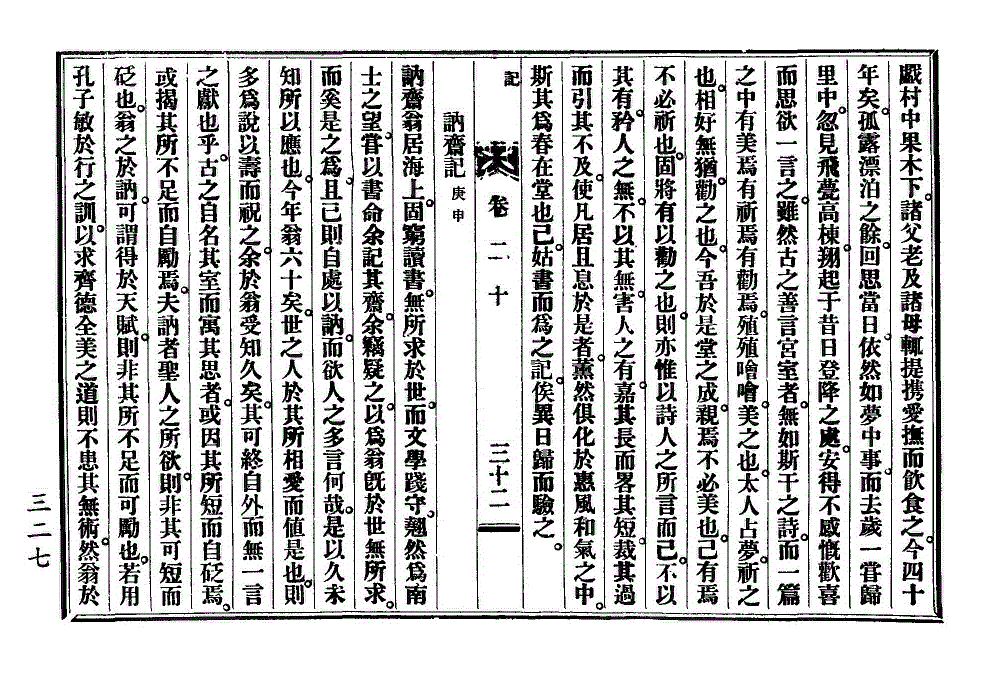 戏村中果木下。诸父老及诸母辄提携爱抚而饮食之。今四十年矣。孤露漂泊之馀。回思当日。依然如梦中事。而去岁一尝归里中。忽见飞甍高栋。翔起于昔日登降之处。安得不感慨欢喜而思欲一言之。虽然古之善言宫室者。无如斯干之诗。而一篇之中有美焉有祈焉有劝焉。殖殖哙哙。美之也。太人占梦。祈之也。相好无犹。劝之也。今吾于是堂之成。亲焉不必美也。已有焉不必祈也。固将有以劝之也。则亦惟以诗人之所言而已。不以其有。矜人之无。不以其无。害人之有。嘉其长而略其短。裁其过而引其不及。使凡居且息于是者。薰然俱化于惠风和气之中。斯其为春在堂也已。姑书而为之记。俟异日归而验之。
戏村中果木下。诸父老及诸母辄提携爱抚而饮食之。今四十年矣。孤露漂泊之馀。回思当日。依然如梦中事。而去岁一尝归里中。忽见飞甍高栋。翔起于昔日登降之处。安得不感慨欢喜而思欲一言之。虽然古之善言宫室者。无如斯干之诗。而一篇之中有美焉有祈焉有劝焉。殖殖哙哙。美之也。太人占梦。祈之也。相好无犹。劝之也。今吾于是堂之成。亲焉不必美也。已有焉不必祈也。固将有以劝之也。则亦惟以诗人之所言而已。不以其有。矜人之无。不以其无。害人之有。嘉其长而略其短。裁其过而引其不及。使凡居且息于是者。薰然俱化于惠风和气之中。斯其为春在堂也已。姑书而为之记。俟异日归而验之。讷斋记(庚申)
讷斋翁居海上。固穷读书。无所求于世。而文学践守。翘然为南士之望。尝以书命余记其斋。余窃疑之。以为翁既于世无所求。而奚是之为。且已则自处以讷。而欲人之多言何哉。是以久未知所以应也。今年翁六十矣。世之人于其所相爱而值是也。则多为说以寿而祝之。余于翁受知久矣。其可终自外而无一言之献也乎。古之自名其室而寓其思者。或因其所短而自砭焉。或揭其所不足而自励焉。夫讷者圣人之所欲。则非其可短而砭也。翁之于讷。可谓得于天赋。则非其所不足而可励也。若用孔子敏于行之训。以求齐德全美之道则不患其无术。然翁于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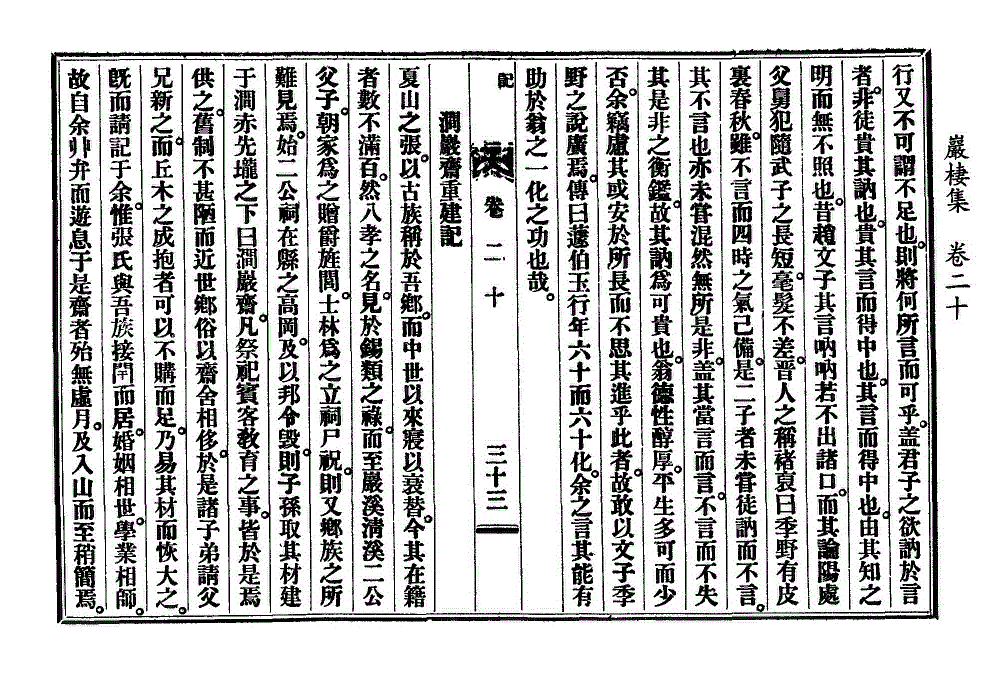 行又不可谓不足也。则将何所言而可乎。盖君子之欲讷于言者。非徒贵其讷也。贵其言而得中也。其言而得中也。由其知之明而无不照也。昔赵文子其言呐呐若不出诸口。而其论阳处父舅犯随武子之长短。毫发不差。晋人之称褚裒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虽不言而四时之气已备。是二子者未尝徒讷而不言。其不言也亦未尝混然无所是非。盖其当言而言。不言而不失其是非之衡鉴。故其讷为可贵也。翁德性醇厚。平生多可而少否。余窃虑其或安于所长而不思其进乎此者。故敢以文子季野之说广焉。传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余之言其能有助于翁之一化之功也哉。
行又不可谓不足也。则将何所言而可乎。盖君子之欲讷于言者。非徒贵其讷也。贵其言而得中也。其言而得中也。由其知之明而无不照也。昔赵文子其言呐呐若不出诸口。而其论阳处父舅犯随武子之长短。毫发不差。晋人之称褚裒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虽不言而四时之气已备。是二子者未尝徒讷而不言。其不言也亦未尝混然无所是非。盖其当言而言。不言而不失其是非之衡鉴。故其讷为可贵也。翁德性醇厚。平生多可而少否。余窃虑其或安于所长而不思其进乎此者。故敢以文子季野之说广焉。传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余之言其能有助于翁之一化之功也哉。涧岩斋重建记
夏山之张。以古族称于吾乡。而中世以来寝以衰替。今其在籍者数不满百。然八孝之名。见于锡类之禄。而至岩溪清溪二公父子。朝家为之赠爵旌闾。士林为之立祠尸祝。则又乡族之所难见焉。始二公祠在县之高冈。及以邦令毁。则子孙取其材建于涧赤先垄之下曰涧岩斋。凡祭祀宾客教育之事。皆于是焉供之。旧制不甚陋而近世乡俗以斋舍相侈。于是诸子弟请父兄新之。而丘木之成抱者可以不购而足。乃易其材而恢大之。既而请记于余。惟张氏与吾族接闬而居。婚姻相世。学业相师。故自余丱弁而游息于是斋者殆无虚月。及入山而至稍简焉。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8L 页
 迨其新构之成而仅一再至焉。然至则未尝不为之顾眄而欣畅。则其早夜起居息偃于斯者可知矣。然观近世之人。其于事神便人之道。文日益备。事日益修。视其先人所为。若将加之而又矜焉者。而其至诚纯质先实而后名。终有未及于古人者。方二公之力行以事亲也。其心岂肯以便于己而耀乎外哉。而卒能动天地协人心而有不磨之名者。则惟其质与实也。今张氏之事。弥乎文矣。然未可以此而自多也。反而求之于实。则有不远之则在焉。以是恢而大之。亹亹而不已焉。则振衰返兴回替为隆。由此其机也。岂但以古族见称于吾乡而已哉。
迨其新构之成而仅一再至焉。然至则未尝不为之顾眄而欣畅。则其早夜起居息偃于斯者可知矣。然观近世之人。其于事神便人之道。文日益备。事日益修。视其先人所为。若将加之而又矜焉者。而其至诚纯质先实而后名。终有未及于古人者。方二公之力行以事亲也。其心岂肯以便于己而耀乎外哉。而卒能动天地协人心而有不磨之名者。则惟其质与实也。今张氏之事。弥乎文矣。然未可以此而自多也。反而求之于实。则有不远之则在焉。以是恢而大之。亹亹而不已焉。则振衰返兴回替为隆。由此其机也。岂但以古族见称于吾乡而已哉。溯真亭记
嘉树之北绀岳之下。有铺渊焉。以泉石名。俗呼曰加每渊。加每者。东语釜之译也。故或以为铺渊者。釜渊之误也。昔南冥曹先生尝风浴于是渊。有诗一绝。而故弘文著作养性轩都公次其韵。今在遗集中可考也。公之后孙居渊之旁。为之作亭以存其思。取公诗中之语以溯真名之而请余记。余惟子孙之于父祖。苟其尝所玩好者。必思护传之爱也。后生之于先贤。苟其尝所经过者。必思表章之敬也。况此泉石之奇。非特玩好之比。而祖先之贤。不止于他人之可敬欤。是亭之作也固宜。抑是渊之著闻也。盖以有冥翁之迹。而公则特为之附庸。乃今亭之作。专主于公而不属于冥翁。是虽以子孙之居近易为力。而于事理则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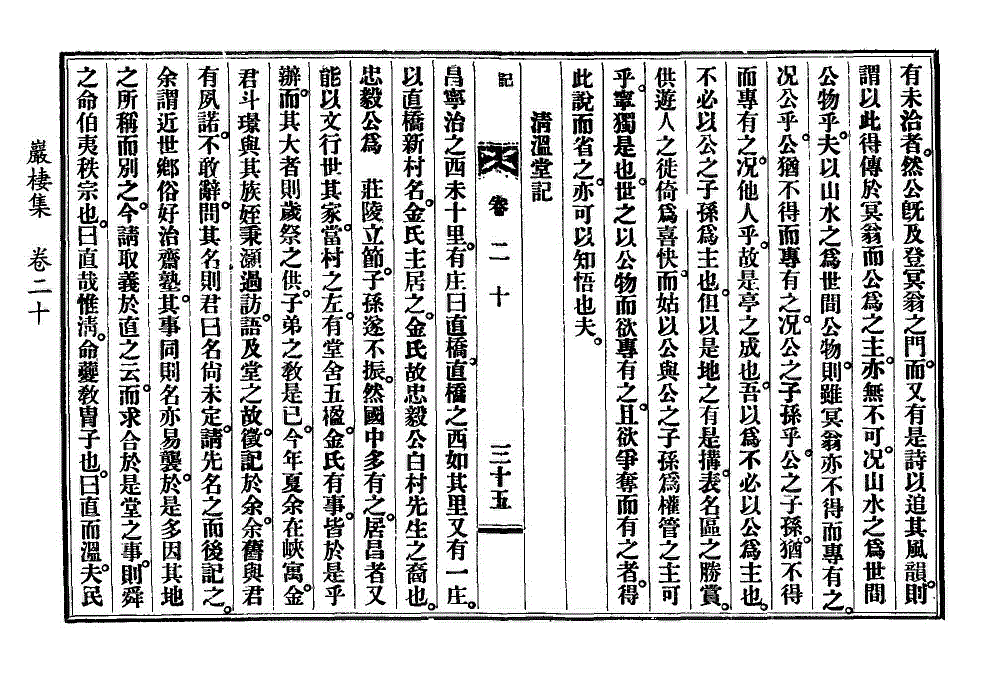 有未洽者。然公既及登冥翁之门。而又有是诗以追其风韵。则谓以此得传于冥翁而公为之主。亦无不可。况山水之为世间公物乎。夫以山水之为世间公物。则虽冥翁亦不得而专有之。况公乎。公犹不得而专有之。况公之子孙乎。公之子孙。犹不得而专有之。况他人乎。故是亭之成也。吾以为不必以公为主也。不必以公之子孙为主也。但以是地之有是搆。表名区之胜赏。供游人之徙倚为喜快。而姑以公与公之子孙为权管之主可乎。宁独是也。世之以公物而欲专有之。且欲争夺而有之者。得此说而省之。亦可以知悟也夫。
有未洽者。然公既及登冥翁之门。而又有是诗以追其风韵。则谓以此得传于冥翁而公为之主。亦无不可。况山水之为世间公物乎。夫以山水之为世间公物。则虽冥翁亦不得而专有之。况公乎。公犹不得而专有之。况公之子孙乎。公之子孙。犹不得而专有之。况他人乎。故是亭之成也。吾以为不必以公为主也。不必以公之子孙为主也。但以是地之有是搆。表名区之胜赏。供游人之徙倚为喜快。而姑以公与公之子孙为权管之主可乎。宁独是也。世之以公物而欲专有之。且欲争夺而有之者。得此说而省之。亦可以知悟也夫。清温堂记
昌宁治之西未十里。有庄曰直桥。直桥之西如其里又有一庄。以直桥新村名。金氏主居之。金氏故忠毅公白村先生之裔也。忠毅公为 庄陵立节。子孙遂不振。然国中多有之。居昌者又能以文行世其家。当村之左。有堂舍五楹。金氏有事。皆于是乎办。而其大者则岁祭之供。子弟之教是已。今年夏余在峡寓。金君斗璟与其族侄秉灏过访。语及堂之故。徵记于余。余旧与君有夙诺。不敢辞。问其名则君曰名尚未定。请先名之而后记之。余谓近世乡俗好治斋塾。其事同则名亦易袭。于是多因其地之所称而别之。今请取义于直之云。而求合于是堂之事。则舜之命伯夷秩宗也。曰直哉惟清。命夔教胄子也。曰直而温。夫民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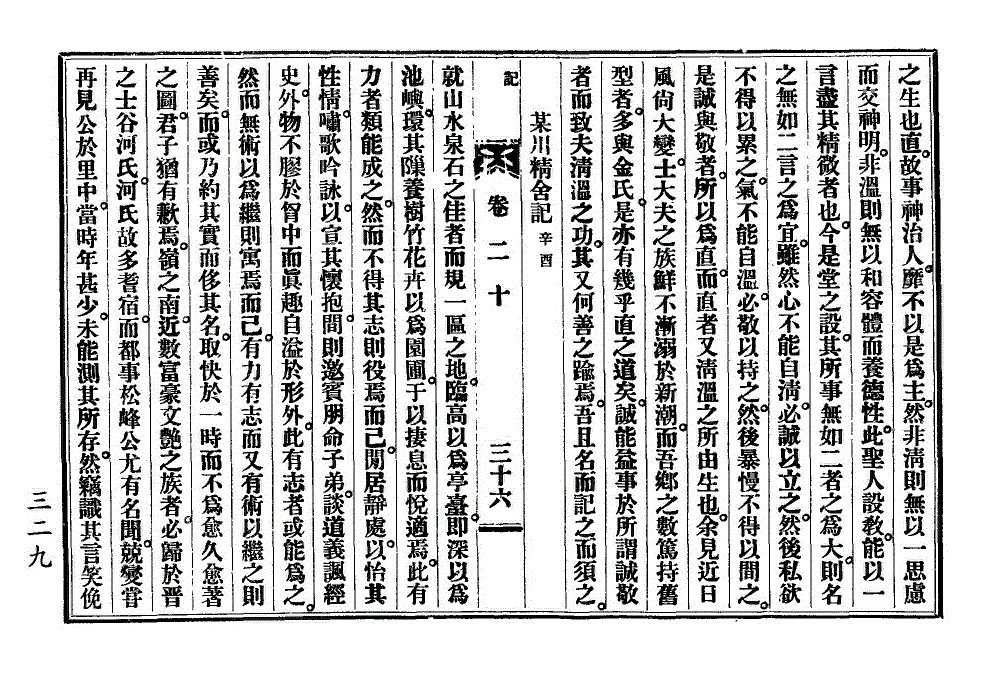 之生也直。故事神治人。靡不以是为主。然非清则无以一思虑而交神明。非温则无以和容体而养德性。此圣人设教。能以一言尽其精微者也。今是堂之设。其所事无如二者之为大。则名之无如二言之为宜。虽然心不能自清。必诚以立之。然后私欲不得以累之。气不能自温。必敬以持之。然后暴慢不得以间之。是诚与敬者。所以为直。而直者又清温之所由生也。余见近日风尚大变。士大夫之族鲜不渐溺于新潮。而吾乡之数笃持旧型者。多与金氏。是亦有几乎直之道矣。诚能益事于所谓诚敬者而致夫清温之功。其又何善之踰焉。吾且名而记之而须之。
之生也直。故事神治人。靡不以是为主。然非清则无以一思虑而交神明。非温则无以和容体而养德性。此圣人设教。能以一言尽其精微者也。今是堂之设。其所事无如二者之为大。则名之无如二言之为宜。虽然心不能自清。必诚以立之。然后私欲不得以累之。气不能自温。必敬以持之。然后暴慢不得以间之。是诚与敬者。所以为直。而直者又清温之所由生也。余见近日风尚大变。士大夫之族鲜不渐溺于新潮。而吾乡之数笃持旧型者。多与金氏。是亦有几乎直之道矣。诚能益事于所谓诚敬者而致夫清温之功。其又何善之踰焉。吾且名而记之而须之。某川精舍记(辛酉)
就山水泉石之佳者而规一区之地。临高以为亭台。即深以为池屿。环其隙养树竹花卉以为园圃。于以栖息而悦适焉。此有力者类能成之。然而不得其志则役焉而已。閒居静处。以怡其性情。啸歌吟咏。以宣其怀抱。间则邀宾朋命子弟。谈道义讽经史。外物不胶于胸中而真趣自溢于形外。此有志者或能为之。然而无术以为继则寓焉而已。有力有志而又有术以继之则善矣。而或乃约其实而侈其名。取快于一时而不为愈久愈著之图。君子犹有歉焉。岭之南。近数富豪文艳之族者。必归于晋之士谷河氏。河氏故多耆宿。而都事松峰公尤有名闻。兢燮尝再见公于里中。当时年甚少。未能测其所存。然窃识其言笑俛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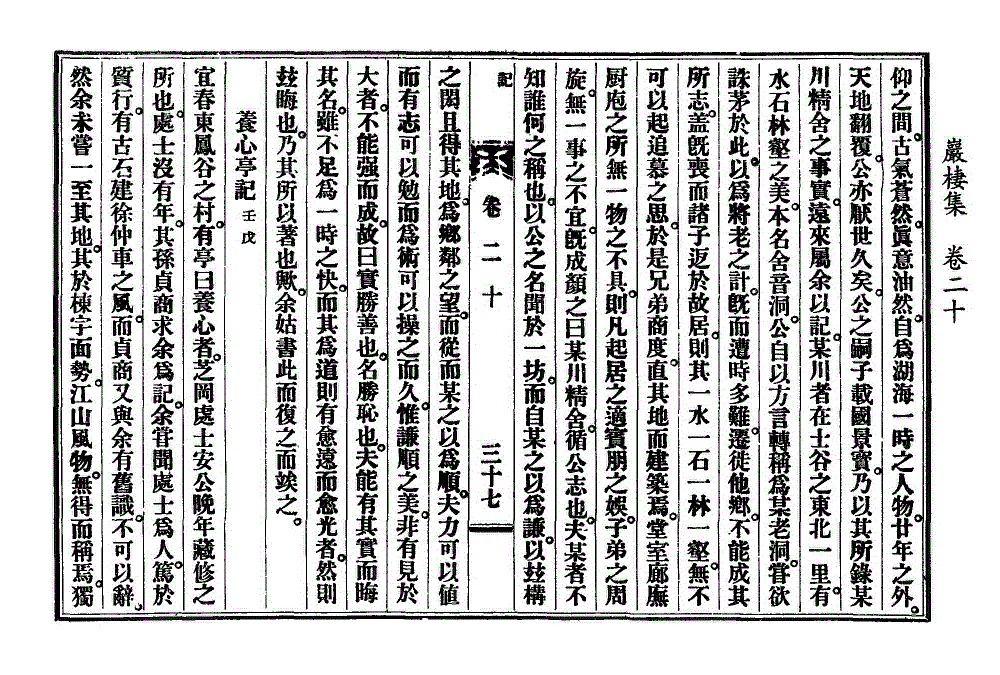 仰之间。古气苍然。真意油然。自为湖海一时之人物。廿年之外。天地翻覆。公亦厌世久矣。公之嗣子载国景宝。乃以其所录某川精舍之事实。远来属余以记。某川者在士谷之东北一里。有水石林壑之美。本名舍音洞。公自以方言转称为某老洞。尝欲诛茅于此。以为将老之计。既而遭时多难。迁徙他乡。不能成其所志。盖既丧而诸子返于故居。则其一水一石一林一壑。无不可以起追慕之思。于是兄弟商度。直其地而建筑焉。堂室廊庑厨庖之所无一物之不具。则凡起居之适宾朋之娱。子弟之周旋。无一事之不宜。既成颜之曰某川精舍。循公志也。夫某者不知谁何之称也。以公之名闻于一坊。而自某之以为谦。以玆构之闳且得其地。为乡邻之望。而从而某之以为顺。夫力可以值而有志可以勉而为术可以操之而久。惟谦顺之美。非有见于大者。不能强而成。故曰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夫能有其实而晦其名。虽不足为一时之快。而其为道则有愈远而愈光者。然则玆晦也。乃其所以著也欤。余姑书此而复之而俟之。
仰之间。古气苍然。真意油然。自为湖海一时之人物。廿年之外。天地翻覆。公亦厌世久矣。公之嗣子载国景宝。乃以其所录某川精舍之事实。远来属余以记。某川者在士谷之东北一里。有水石林壑之美。本名舍音洞。公自以方言转称为某老洞。尝欲诛茅于此。以为将老之计。既而遭时多难。迁徙他乡。不能成其所志。盖既丧而诸子返于故居。则其一水一石一林一壑。无不可以起追慕之思。于是兄弟商度。直其地而建筑焉。堂室廊庑厨庖之所无一物之不具。则凡起居之适宾朋之娱。子弟之周旋。无一事之不宜。既成颜之曰某川精舍。循公志也。夫某者不知谁何之称也。以公之名闻于一坊。而自某之以为谦。以玆构之闳且得其地。为乡邻之望。而从而某之以为顺。夫力可以值而有志可以勉而为术可以操之而久。惟谦顺之美。非有见于大者。不能强而成。故曰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夫能有其实而晦其名。虽不足为一时之快。而其为道则有愈远而愈光者。然则玆晦也。乃其所以著也欤。余姑书此而复之而俟之。养心亭记(壬戌)
宜春东凤谷之村。有亭曰养心者。芝冈处士安公晚年藏修之所也。处士没有年。其孙贞商求余为记。余尝闻处士为人。笃于质行。有古石建徐仲车之风。而贞商又与余有旧识。不可以辞。然余未尝一至其地。其于栋宇面势。江山风物。无得而称焉。独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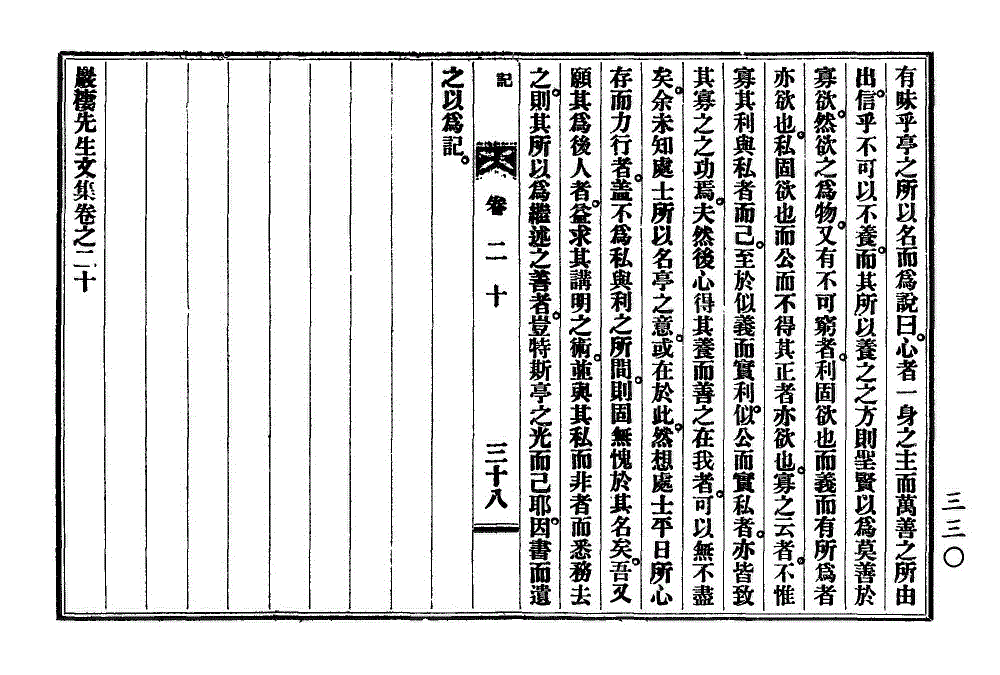 有味乎亭之所以名而为说曰。心者一身之主而万善之所由出。信乎不可以不养。而其所以养之之方则圣贤以为莫善于寡欲。然欲之为物。又有不可穷者。利固欲也而义而有所为者亦欲也。私固欲也而公而不得其正者亦欲也。寡之云者。不惟寡其利与私者而已。至于似义而实利。似公而实私者。亦皆致其寡之之功焉。夫然后心得其养而善之在我者。可以无不尽矣。余未知处士所以名亭之意。或在于此。然想处士平日所心存而力行者。盖不为私与利之所间。则固无愧于其名矣。吾又愿其为后人者。益求其讲明之术。并与其私而非者而悉务去之。则其所以为继述之善者。岂特斯亭之光而已耶。因书而遗之以为记。
有味乎亭之所以名而为说曰。心者一身之主而万善之所由出。信乎不可以不养。而其所以养之之方则圣贤以为莫善于寡欲。然欲之为物。又有不可穷者。利固欲也而义而有所为者亦欲也。私固欲也而公而不得其正者亦欲也。寡之云者。不惟寡其利与私者而已。至于似义而实利。似公而实私者。亦皆致其寡之之功焉。夫然后心得其养而善之在我者。可以无不尽矣。余未知处士所以名亭之意。或在于此。然想处士平日所心存而力行者。盖不为私与利之所间。则固无愧于其名矣。吾又愿其为后人者。益求其讲明之术。并与其私而非者而悉务去之。则其所以为继述之善者。岂特斯亭之光而已耶。因书而遗之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