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x 页
明美堂集卷十二(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跋
跋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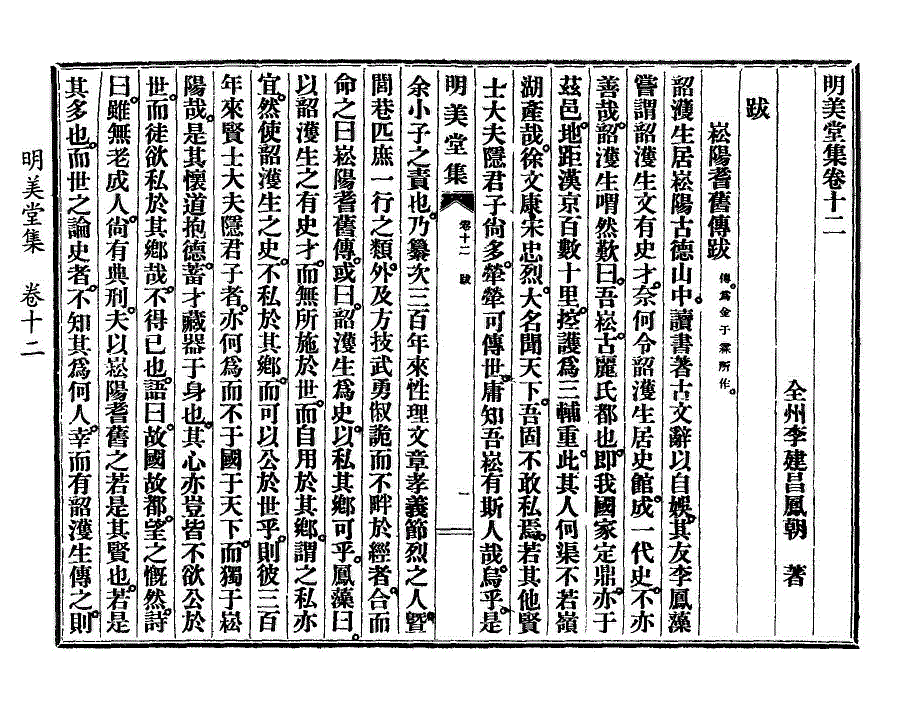 崧阳耆旧传跋(传。为金于霖所作。)
崧阳耆旧传跋(传。为金于霖所作。)韶濩生居崧阳古德山中。读书著古文辞以自娱。其友李凤藻尝谓韶濩生文有史才。奈何令韶濩生居史馆。成一代史。不亦善哉。韶濩生喟然叹曰。吾崧。古丽氏都也。即我国家定鼎。亦于兹邑。地距汉京百数十里。控护为三辅重。此其人何渠不若岭湖产哉。徐文康,宋忠烈。大名闻天下。吾固不敢私焉。若其他贤士大夫隐君子尚多。荦荦可传世。庸知吾崧有斯人哉。乌乎。是余小子之责也。乃纂次三百年来性理文章孝义节烈之人。暨闾巷匹庶一行之类。外及方技武勇俶诡而不畔于经者。合而命之曰崧阳耆旧传。或曰。韶濩生为史。以私其乡可乎。凤藻曰。以韶濩生之有史才。而无所施于世。而自用于其乡。谓之私亦宜。然使韶濩生之史。不私于其乡。而可以公于世乎。则彼三百年来贤士大夫隐君子者。亦何为而不于国于天下。而独于崧阳哉。是其怀道抱德。蓄才藏器于身也。其心亦岂皆不欲公于世。而徒欲私于其乡哉。不得已也。语曰。故国故都。望之慨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夫以崧阳耆旧之若是其贤也。若是其多也。而世之论史者。不知其为何人。幸而有韶濩生传之。则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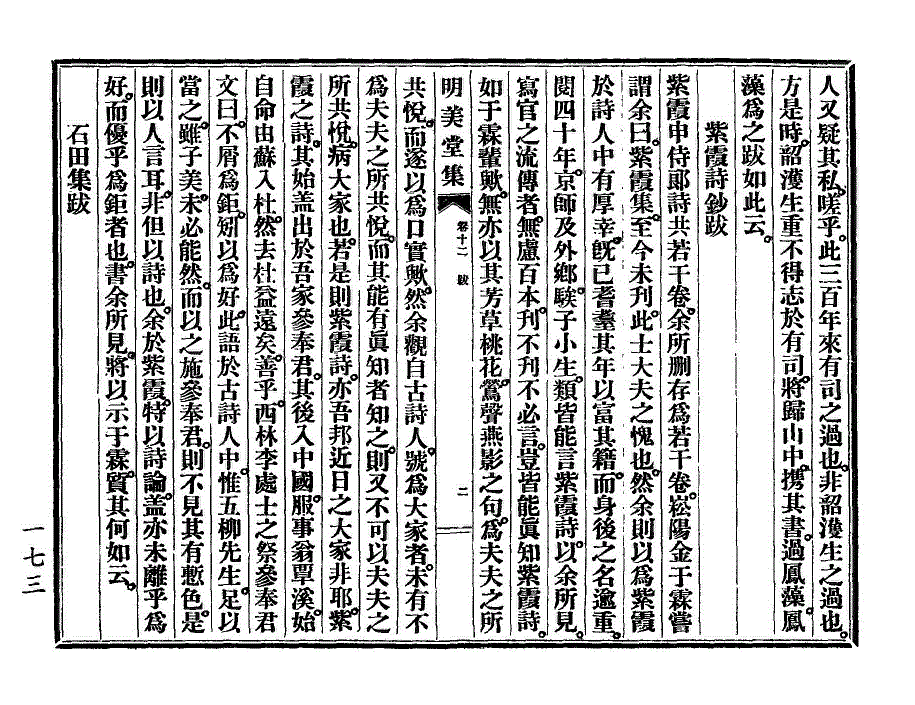 人又疑其私。嗟乎。此三百年来有司之过也。非韶濩生之过也。方是时。韶濩生重不得志于有司。将归山中。携其书。过凤藻。凤藻为之跋如此云。
人又疑其私。嗟乎。此三百年来有司之过也。非韶濩生之过也。方是时。韶濩生重不得志于有司。将归山中。携其书。过凤藻。凤藻为之跋如此云。紫霞诗钞跋
紫霞申侍郎诗共若干卷。余所删存为若干卷。崧阳金于霖尝谓余曰。紫霞集。至今未刊。此士大夫之愧也。然余则以为紫霞于诗人中有厚幸。既已耆耋其年以富其籍。而身后之名逾重。阅四十年。京师及外乡。騃子小生。类皆能言紫霞诗。以余所见。写官之流传者。无虑百本。刊不刊不必言。岂皆能真知紫霞诗。如于霖辈欤。无亦以其芳草桃花。莺声燕影之句。为夫夫之所共悦。而遂以为口实欤。然余观自古诗人。号为大家者。未有不为夫夫之所共悦。而其能有真知者知之。则又不可以夫夫之所共悦。病大家也。若是则紫霞诗。亦吾邦近日之大家非耶。紫霞之诗。其始盖出于吾家参奉君。其后入中国。服事翁覃溪。始自命由苏入杜。然去杜益远矣。善乎。西林李处士之祭参奉君文曰。不屑为钜。矧以为好。此语于古诗人中。惟五柳先生。足以当之。虽子美。未必能然。而以之施参奉君。则不见其有惭色。是则以人言耳。非但以诗也。余于紫霞。特以诗论。盖亦未离乎为好。而优乎为钜者也。书余所见。将以示于霖。质其何如云。
石田集跋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4H 页
 某既为石田公。志其幽堂矣。而公之子承鹤子和。复以公所著诗文集。属余校编。余时方谪贝州。日与湖南之士相交游。因以得闻其有识之定论。以是益知向之所为志。庶可以无愧色。而及校公诗文。益信公非徒辞为者为之。感叹不能已。而子和则曰。先人之于文艺。盖以为未能也。故所收录亦不多。今以斯文蕲必传。则非先人之意也。庸以尽吾后人之心已耳。余谓不然。自余来此。见近日枣梨之锓者。多矣。罕有见如斯集者也。人生于三。天下之大纲。读公考妣阡表。知公之孝亲也。读公祭芦沙文。见公之尊师也。若三政策讨洋人檄。祭我祖忠贞公文。余既以其事载之于公之志。而尤见公之忠君爱国。畎亩而不忘。板荡而愈奋。慨然有节义之风。余又有志之所未载。而于斯集始徵之。复从子和之子光秀。而得其详者。光秀告余曰。光秀年十岁。尚记先大父闻京师军变。发声恸哭。涕泗被面。光秀窃怪吾祖一布衣。何至如此。今集中所载上三从兄正言所云。当千古所无之变。重有内外之忧。兄之自处。不可出一足于都门之外。滔滔此世。惟恐为俗所误者。乃其时书也。呜呼。滔滔者胡可言哉。内有贼而不能讨。外有寇而不知戒。挈孥载货。逃难以求免者相属于途。而又其甚。则苟焉徼一时之利。暋然若平常。虽谓之举朝无人。可也。以至于今。虽有出一言效一事。为国忱诚者。而苛覈之论。辄曰。何前之寥寥。而今之聒聒也。此说一出。虽善
某既为石田公。志其幽堂矣。而公之子承鹤子和。复以公所著诗文集。属余校编。余时方谪贝州。日与湖南之士相交游。因以得闻其有识之定论。以是益知向之所为志。庶可以无愧色。而及校公诗文。益信公非徒辞为者为之。感叹不能已。而子和则曰。先人之于文艺。盖以为未能也。故所收录亦不多。今以斯文蕲必传。则非先人之意也。庸以尽吾后人之心已耳。余谓不然。自余来此。见近日枣梨之锓者。多矣。罕有见如斯集者也。人生于三。天下之大纲。读公考妣阡表。知公之孝亲也。读公祭芦沙文。见公之尊师也。若三政策讨洋人檄。祭我祖忠贞公文。余既以其事载之于公之志。而尤见公之忠君爱国。畎亩而不忘。板荡而愈奋。慨然有节义之风。余又有志之所未载。而于斯集始徵之。复从子和之子光秀。而得其详者。光秀告余曰。光秀年十岁。尚记先大父闻京师军变。发声恸哭。涕泗被面。光秀窃怪吾祖一布衣。何至如此。今集中所载上三从兄正言所云。当千古所无之变。重有内外之忧。兄之自处。不可出一足于都门之外。滔滔此世。惟恐为俗所误者。乃其时书也。呜呼。滔滔者胡可言哉。内有贼而不能讨。外有寇而不知戒。挈孥载货。逃难以求免者相属于途。而又其甚。则苟焉徼一时之利。暋然若平常。虽谓之举朝无人。可也。以至于今。虽有出一言效一事。为国忱诚者。而苛覈之论。辄曰。何前之寥寥。而今之聒聒也。此说一出。虽善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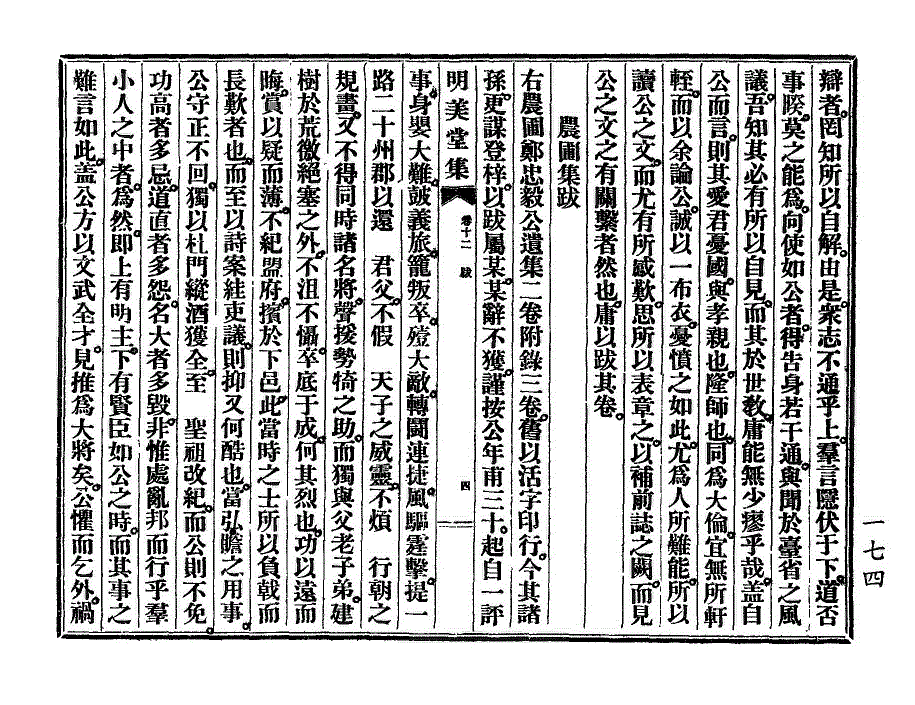 辩者。罔知所以自解。由是。众志不通乎上。群言隐伏于下。道否事暌。莫之能为。向使如公者。得告身若干通。与闻于台省之风议。吾知其必有所以自见。而其于世教。庸能无少瘳乎哉。盖自公而言。则其爱君忧国。与孝亲也。隆师也。同为大伦。宜无所轩轾。而以余论公。诚以一布衣。忧愤之如此。尤为人所难能。所以读公之文。而尤有所感叹。思所以表章之。以补前志之阙。而见公之文之有关系者然也。庸以跋其卷。
辩者。罔知所以自解。由是。众志不通乎上。群言隐伏于下。道否事暌。莫之能为。向使如公者。得告身若干通。与闻于台省之风议。吾知其必有所以自见。而其于世教。庸能无少瘳乎哉。盖自公而言。则其爱君忧国。与孝亲也。隆师也。同为大伦。宜无所轩轾。而以余论公。诚以一布衣。忧愤之如此。尤为人所难能。所以读公之文。而尤有所感叹。思所以表章之。以补前志之阙。而见公之文之有关系者然也。庸以跋其卷。农圃集跋
右农圃郑忠毅公遗集二卷附录三卷。旧以活字印行。今其诸孙。更谋登梓。以跋属某。某辞不获。谨按公年甫三十。起自一评事。身婴大难。鼓义旅。笼叛卒。殪大敌。转斗连捷。风驱霆击。提一路二十州郡以还 君父。不假 天子之威灵。不烦 行朝之规画。又不得同时诸名将。声援势犄之助。而独与父老子弟。建树于荒徼绝塞之外。不沮不慑。卒底于成。何其烈也。功以远而晦。赏以疑而薄。不纪盟府。摈于下邑。此当时之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而至以诗案絓吏议。则抑又何酷也。当弘,瞻之用事。公守正不回。独以杜门纵酒获全。至 圣祖改纪。而公则不免。功高者多忌。道直者多怨。名大者多毁。非惟处乱邦而行乎群小人之中者。为然。即上有明主。下有贤臣如公之时。而其事之难言如此。盖公方以文武全才。见推为大将矣。公惧而乞外。祸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5H 页
 踵而作。士不患不见知。患于见知。不忧不见用。忧于见用。夫见知且用。至号为文武才。而待之以将帅者。此其势亦迫矣。岂逡巡回翔之所。可得以解哉。昔李伯纪论陆敬舆。深羡其忠著功验。虽贬死。可以无恨。其言至为痛功(一作切)。千载之下。读公之文。而感公之事。将有如伯纪之于敬舆者。区区荣辱死生。不足以为公惜也。抑余尝考公之功。其关系甚钜。而前贤之纪述。尚或未有以尽发之者。秀吉之枭将。无如清正。世称清正与行长。分阄赌战。清正得北。故入咸镜。此传者之误耳。岂有用兵而戏者乎。凡兵事先北而后南。我国之形。以北为首。且兴王之地也。秀吉之遣清正。将以抗我之根柢。而纵兵四下。乘建瓴之便。可以无所往而不获。此其本谋也。向微公出死力以遏其锋。北路不可复而中兴无日矣。且北路迩于羯。彼其耽眈久矣。伺我之难。而思逞其图。明朝之为我计者。亦尝已虑之矣。况景仁末秀辈。土着之雄。连结有素。其叛虽附倭。实亦左右足者也。公巡行六镇。以绥杂种。威信所及。至还其所掠人口。而帖然不敢复动。苟非然者。清正虽遁。叛者且将北附矣。方公没而建州炽驯。至丙丁而极。使公无当日之勋。焉知南北之衅。不并发于一时。而不待四十年之后耶。由此言之。公之功存社稷。又岂仅一北路哉。此尚论者之所不可不知也。公诗文虽不多。其辞皆高亮激越。明白真挚。即以文章言。亦足以自传。至其所谓诗案。当时已以为无
踵而作。士不患不见知。患于见知。不忧不见用。忧于见用。夫见知且用。至号为文武才。而待之以将帅者。此其势亦迫矣。岂逡巡回翔之所。可得以解哉。昔李伯纪论陆敬舆。深羡其忠著功验。虽贬死。可以无恨。其言至为痛功(一作切)。千载之下。读公之文。而感公之事。将有如伯纪之于敬舆者。区区荣辱死生。不足以为公惜也。抑余尝考公之功。其关系甚钜。而前贤之纪述。尚或未有以尽发之者。秀吉之枭将。无如清正。世称清正与行长。分阄赌战。清正得北。故入咸镜。此传者之误耳。岂有用兵而戏者乎。凡兵事先北而后南。我国之形。以北为首。且兴王之地也。秀吉之遣清正。将以抗我之根柢。而纵兵四下。乘建瓴之便。可以无所往而不获。此其本谋也。向微公出死力以遏其锋。北路不可复而中兴无日矣。且北路迩于羯。彼其耽眈久矣。伺我之难。而思逞其图。明朝之为我计者。亦尝已虑之矣。况景仁末秀辈。土着之雄。连结有素。其叛虽附倭。实亦左右足者也。公巡行六镇。以绥杂种。威信所及。至还其所掠人口。而帖然不敢复动。苟非然者。清正虽遁。叛者且将北附矣。方公没而建州炽驯。至丙丁而极。使公无当日之勋。焉知南北之衅。不并发于一时。而不待四十年之后耶。由此言之。公之功存社稷。又岂仅一北路哉。此尚论者之所不可不知也。公诗文虽不多。其辞皆高亮激越。明白真挚。即以文章言。亦足以自传。至其所谓诗案。当时已以为无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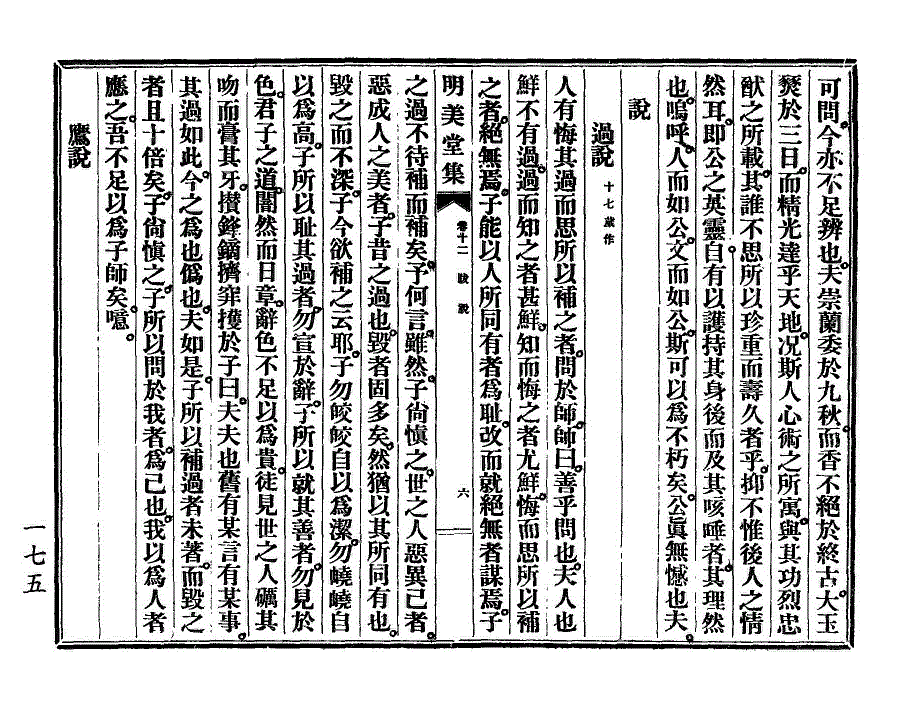 可问。今亦不足辨也。夫崇兰委于九秋。而香不绝于终古。大玉燹于三日。而精光达乎天地。况斯人心术之所寓。与其功烈忠猷之所载。其谁不思所以珍重而寿久者乎。抑不惟后人之情然耳。即公之英灵。自有以护持其身后而及其咳唾者。其理然也。呜呼。人而如公。文而如公。斯可以为不朽矣。公真无憾也夫。
可问。今亦不足辨也。夫崇兰委于九秋。而香不绝于终古。大玉燹于三日。而精光达乎天地。况斯人心术之所寓。与其功烈忠猷之所载。其谁不思所以珍重而寿久者乎。抑不惟后人之情然耳。即公之英灵。自有以护持其身后而及其咳唾者。其理然也。呜呼。人而如公。文而如公。斯可以为不朽矣。公真无憾也夫。明美堂集卷十二(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说
过说(十七岁作)
人有悔其过而思所以补之者。问于师。师曰。善乎问也。夫人也鲜不有过。过而知之者甚鲜。知而悔之者尤鲜。悔而思所以补之者。绝无焉。子能以人所同有者为耻。改而就绝无者谋焉。子之过不待补而补矣。予何言。虽然。子尚慎之。世之人恶异己者。恶成人之美者。子昔之过也。毁者固多矣。然犹以其所同有也。毁之而不深。子今欲补之云耶。子勿皎皎自以为洁。勿峣峣自以为高。子所以耻其过者。勿宣于辞。子所以就其善者。勿见于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辞色不足以为贵。徒见世之人砺其吻而膏其牙。攒锋镝挤阱擭于子曰。夫夫也旧有某言有某事。其过如此。今之为也伪也。夫如是。子所以补过者未著。而毁之者且十倍矣。子尚慎之。子所以问于我者。为己也。我以为人者应之。吾不足以为子师矣。噫。
鹰说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6H 页
 凤与鸾之德以文。鹤之德以清。而鹰之德以击。夫击。非所以为德也。然既不为凤为鸾为鹤而为鹰。不彩羽嘉声而有觜与距。是固使之击也。使之击而不击者。是亦不足为凤为鸾为鹤。而又不得为鹰矣。里之人。有获鹰者。献于李子。李子使之猎。登阜而望。鹰方昂首举翼。振迅而顾左右。状若甚厉者。俄而雉兴于前。鹰奋而趋。将禽矣。忽睨而视。踆而却。为之迁延。则雉已疾飞而遁矣。既而兔起于侧。鹰不复奋而趋。视愈平而却愈后。若反有畏然。兔则绥绥然过矣。如是者终日。卒无获。李子曰。恶用是鹰为哉。纵之去。或曰。是鹰也。仁且智矣。可以击而不击。非仁乎。知人之见其不击。则必且纵之。非知乎。不者。且系于此矣。
凤与鸾之德以文。鹤之德以清。而鹰之德以击。夫击。非所以为德也。然既不为凤为鸾为鹤而为鹰。不彩羽嘉声而有觜与距。是固使之击也。使之击而不击者。是亦不足为凤为鸾为鹤。而又不得为鹰矣。里之人。有获鹰者。献于李子。李子使之猎。登阜而望。鹰方昂首举翼。振迅而顾左右。状若甚厉者。俄而雉兴于前。鹰奋而趋。将禽矣。忽睨而视。踆而却。为之迁延。则雉已疾飞而遁矣。既而兔起于侧。鹰不复奋而趋。视愈平而却愈后。若反有畏然。兔则绥绥然过矣。如是者终日。卒无获。李子曰。恶用是鹰为哉。纵之去。或曰。是鹰也。仁且智矣。可以击而不击。非仁乎。知人之见其不击。则必且纵之。非知乎。不者。且系于此矣。传说
有为故宰相铭墓者。盛言孝友睦姻。或訾之曰。大臣以体国为重。非天下所以治乱存亡者。不足以传。奚为是屑屑然哉。余闻之叹曰。是非惟知大臣之体也。亦知文章之体者也。然又不特大臣而已。古之以文传人者。皆未必传于内行也。传人如画人。画人者。画耳目鼻口不可阙。然传神之妙。或不在于耳目鼻口。而往往出于耳目鼻口之外。如所谓眉棱颊毛者。是也。内行犹之。耳目鼻口。人所同也。而若其风神之所在。犹之眉棱颊毛己所独也。故善传人者。必于其人之风神而致意焉。然又不特传人而已。人之所以为人。亦必有人所不尽然。而己能独然者。然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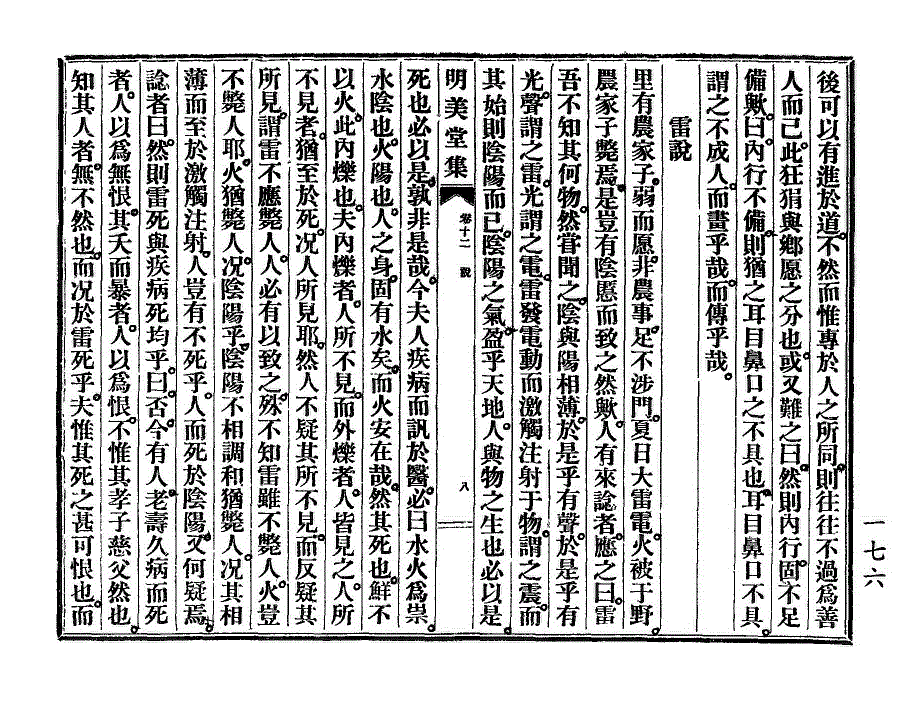 后可以有进于道。不然而惟专于人之所同。则往往不过为善人而已。此狂狷与乡愿之分也。或又难之曰。然则内行。固不足备欤。曰。内行不备。则犹之耳目鼻口之不具也。耳目鼻口不具。谓之不成人。而画乎哉。而传乎哉。
后可以有进于道。不然而惟专于人之所同。则往往不过为善人而已。此狂狷与乡愿之分也。或又难之曰。然则内行。固不足备欤。曰。内行不备。则犹之耳目鼻口之不具也。耳目鼻口不具。谓之不成人。而画乎哉。而传乎哉。雷说
里有农家子。弱而愿。非农事。足不涉门。夏日大雷电。火被于野。农家子毙焉。是岂有阴慝而致之然欤。人有来谂者。应之曰。雷吾不知其何物。然尝闻之。阴与阳相薄。于是乎有声。于是乎有光。声谓之雷。光谓之电。雷发电动而激触注射于物。谓之震。而其始则阴阳而已。阴阳之气。盈乎天地。人与物之生也必以是。死也必以是。孰非是哉。今夫人疾病而訉(一作讯)于医。必曰水火为祟。水阴也。火阳也。人之身。固有水矣。而火安在哉。然其死也。鲜不以火。此内烁也。夫内烁者。人所不见。而外烁者。人皆见之。人所不见者。犹至于死。况人所见耶。然人不疑其所不见。而反疑其所见。谓雷不应毙人。人必有以致之。殊不知雷虽不毙人。火岂不毙人耶。火犹毙人。况阴阳乎。阴阳不相调和犹毙人。况其相薄而至于激触注射。人岂有不死乎。人而死于阴阳。又何疑焉。谂者曰。然则雷死与疾病死均乎。曰。否。今有人。老寿久病而死者。人以为无恨。其夭而暴者。人以为恨。不惟其孝子慈父然也。知其人者。无不然也。而况于雷死乎。夫惟其死之甚可恨也。而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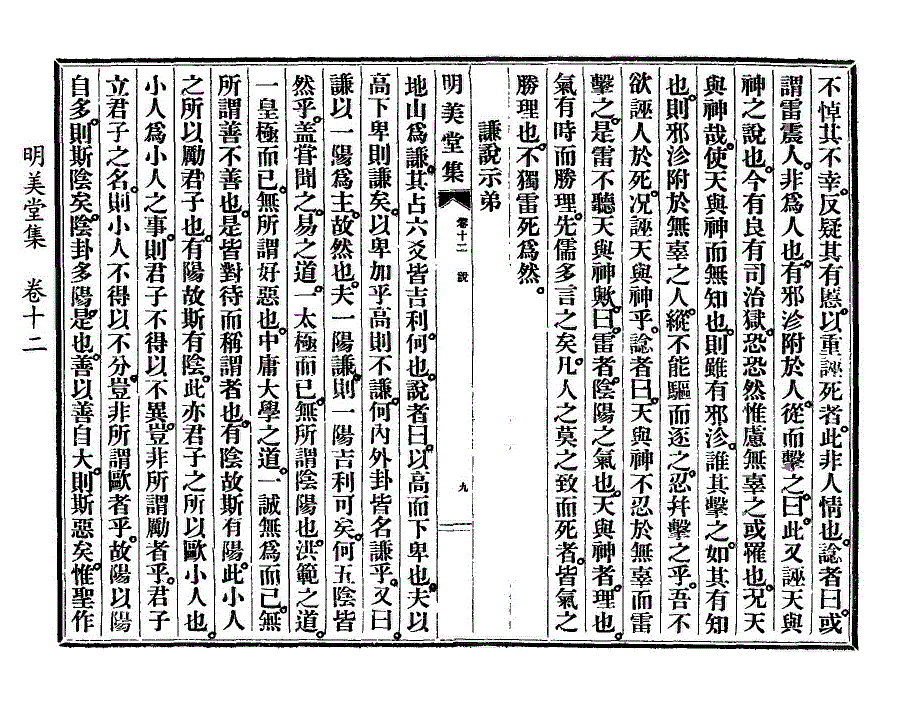 不悼其不幸。反疑其有慝。以重诬死者。此非人情也。谂者曰。或谓雷震人。非为人也。有邪沴附于人。从而击之。曰。此又诬天与神之说也。今有良有司治狱。恐恐然惟虑无辜之或罹也。况天与神哉。使天与神而无知也。则虽有邪沴。谁其击之。如其有知也。则邪沴附于无辜之人。纵不能驱而逐之。忍并击之乎。吾不欲诬人于死。况诬天与神乎。谂者曰。天与神不忍于无辜而雷击之。是雷不听天与神欤。曰。雷者。阴阳之气也。天与神者。理也。气有时而胜理。先儒多言之矣。凡人之莫之致而死者。皆气之胜理也。不独雷死为然。
不悼其不幸。反疑其有慝。以重诬死者。此非人情也。谂者曰。或谓雷震人。非为人也。有邪沴附于人。从而击之。曰。此又诬天与神之说也。今有良有司治狱。恐恐然惟虑无辜之或罹也。况天与神哉。使天与神而无知也。则虽有邪沴。谁其击之。如其有知也。则邪沴附于无辜之人。纵不能驱而逐之。忍并击之乎。吾不欲诬人于死。况诬天与神乎。谂者曰。天与神不忍于无辜而雷击之。是雷不听天与神欤。曰。雷者。阴阳之气也。天与神者。理也。气有时而胜理。先儒多言之矣。凡人之莫之致而死者。皆气之胜理也。不独雷死为然。谦说示弟
地山为谦。其占六爻皆吉利。何也。说者曰。以高而下卑也。夫以高下卑则谦矣。以卑加乎高则不谦。何内外卦皆名谦乎。又曰。谦以一阳为主。故然也。夫一阳谦。则一阳吉利可矣。何五阴皆然乎。盖尝闻之。易之道。一太极而已。无所谓阴阳也。洪范之道。一皇极而已。无所谓好恶也。中庸大学之道。一诚无为而已。无所谓善不善也。是皆对待而称谓者也。有阴故斯有阳。此小人之所以励君子也。有阳故斯有阴。此亦君子之所以欧小人也。小人为小人之事。则君子不得以不异。岂非所谓励者乎。君子立君子之名。则小人不得以不分。岂非所谓欧者乎。故阳以阳自多。则斯阴矣。阴卦多阳。是也。善以善自大。则斯恶矣。惟圣作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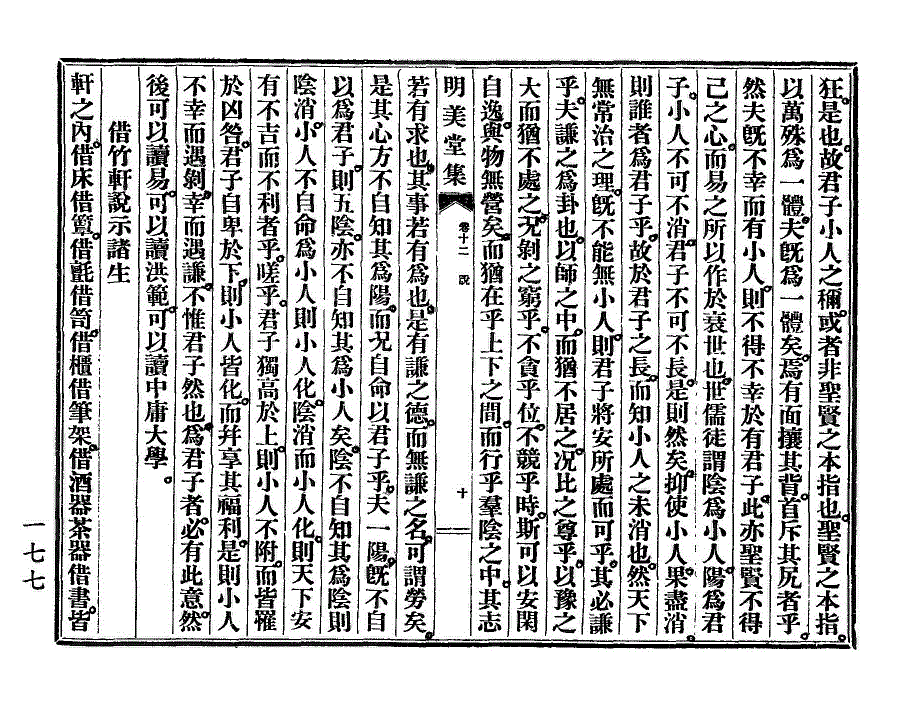 狂。是也。故君子小人之称。或者非圣贤之本指也。圣贤之本指。以万殊为一体。夫既为一体矣。焉有面攘其背。首斥其尻者乎。然夫既不幸而有小人。则不得不幸于有君子。此亦圣贤不得已之心。而易之所以作于衰世也。世儒徒谓阴为小人。阳为君子。小人不可不消。君子不可不长。是则然矣。抑使小人。果尽消。则谁者为君子乎。故于君子之长。而知小人之未消也。然天下无常治之理。既不能无小人。则君子将安所处而可乎。其必谦乎。夫谦之为卦也。以师之中。而犹不居之。况比之尊乎。以豫之大而犹不处之。况剥之穷乎。不贪乎位。不竞乎时。斯可以安闲自逸。与物无营矣。而犹在乎上下之间。而行乎群阴之中。其志若有求也。其事若有为也。是有谦之德。而无谦之名。可谓劳矣。是其心方不自知其为阳。而况自命以君子乎。夫一阳。既不自以为君子。则五阴。亦不自知其为小人矣。阴不自知其为阴则阴消。小人不自命为小人则小人化。阴消而小人化。则天下安有不吉而不利者乎。嗟乎。君子独高于上。则小人不附。而皆罹于凶咎。君子自卑于下。则小人皆化。而并享其福利。是则小人不幸而遇剥。幸而遇谦。不惟君子然也。为君子者。必有此意。然后可以读易。可以读洪范。可以读中庸大学。
狂。是也。故君子小人之称。或者非圣贤之本指也。圣贤之本指。以万殊为一体。夫既为一体矣。焉有面攘其背。首斥其尻者乎。然夫既不幸而有小人。则不得不幸于有君子。此亦圣贤不得已之心。而易之所以作于衰世也。世儒徒谓阴为小人。阳为君子。小人不可不消。君子不可不长。是则然矣。抑使小人。果尽消。则谁者为君子乎。故于君子之长。而知小人之未消也。然天下无常治之理。既不能无小人。则君子将安所处而可乎。其必谦乎。夫谦之为卦也。以师之中。而犹不居之。况比之尊乎。以豫之大而犹不处之。况剥之穷乎。不贪乎位。不竞乎时。斯可以安闲自逸。与物无营矣。而犹在乎上下之间。而行乎群阴之中。其志若有求也。其事若有为也。是有谦之德。而无谦之名。可谓劳矣。是其心方不自知其为阳。而况自命以君子乎。夫一阳。既不自以为君子。则五阴。亦不自知其为小人矣。阴不自知其为阴则阴消。小人不自命为小人则小人化。阴消而小人化。则天下安有不吉而不利者乎。嗟乎。君子独高于上。则小人不附。而皆罹于凶咎。君子自卑于下。则小人皆化。而并享其福利。是则小人不幸而遇剥。幸而遇谦。不惟君子然也。为君子者。必有此意。然后可以读易。可以读洪范。可以读中庸大学。借竹轩说示诸生
轩之内。借床借簟。借毡借笥。借匮借笔架。借酒器茶器借书。皆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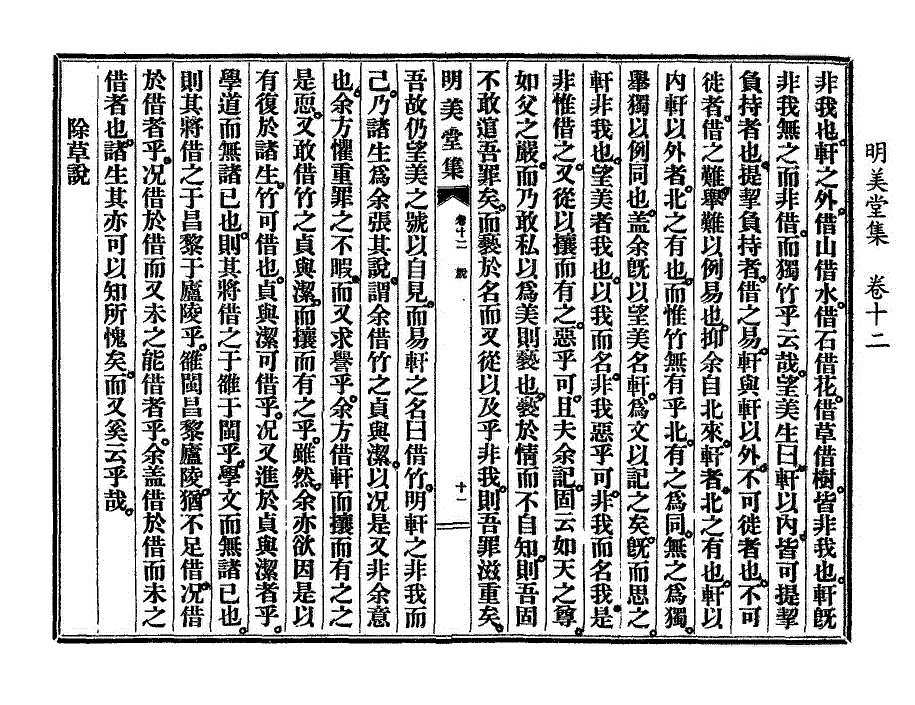 非我也。轩之外。借山借水。借石借花。借草借树。皆非我也。轩既非我无之而非借。而独竹乎云哉。望美生曰。轩以内。皆可提挈负持者也。提挈负持者。借之易。轩与轩以外。不可徙者也。不可徙者。借之难。举难以例易也。抑余自北来。轩者。北之有也。轩以内轩以外者。北之有也。而惟竹无有乎北。有之为同。无之为独。举独以例同也。盖余既以望美名轩。为文以记之矣。既而思之。轩非我也。望美者我也。以我而名。非我恶乎可。非我而名我。是非惟借之。又从以攘而有之。恶乎可。且夫余记。固云如天之尊。如父之严。而乃敢私以为美则亵也。亵于情而不自知。则吾固不敢逭吾罪矣。而亵于名而又从以及乎非我。则吾罪滋重矣。吾故仍望美之号以自见。而易轩之名曰借竹。明轩之非我而已。乃诸生为余张其说。谓余借竹之贞与洁。以况是又非余意也。余方惧重罪之不暇。而又求誉乎。余方借轩而攘而有之之是恧。又敢借竹之贞与洁。而攘而有之乎。虽然。余亦欲因是以有复于诸生。竹可借也。贞与洁可借乎。况又进于贞与洁者乎。学道而无诸己也。则其将借之于雒于闽乎。学文而无诸己也。则其将借之于昌黎于庐陵乎。雒闽昌黎庐陵。犹不足借。况借于借者乎。况借于借而又未之能借者乎。余盖借于借而未之借者也。诸生其亦可以知所愧矣。而又奚云乎哉。
非我也。轩之外。借山借水。借石借花。借草借树。皆非我也。轩既非我无之而非借。而独竹乎云哉。望美生曰。轩以内。皆可提挈负持者也。提挈负持者。借之易。轩与轩以外。不可徙者也。不可徙者。借之难。举难以例易也。抑余自北来。轩者。北之有也。轩以内轩以外者。北之有也。而惟竹无有乎北。有之为同。无之为独。举独以例同也。盖余既以望美名轩。为文以记之矣。既而思之。轩非我也。望美者我也。以我而名。非我恶乎可。非我而名我。是非惟借之。又从以攘而有之。恶乎可。且夫余记。固云如天之尊。如父之严。而乃敢私以为美则亵也。亵于情而不自知。则吾固不敢逭吾罪矣。而亵于名而又从以及乎非我。则吾罪滋重矣。吾故仍望美之号以自见。而易轩之名曰借竹。明轩之非我而已。乃诸生为余张其说。谓余借竹之贞与洁。以况是又非余意也。余方惧重罪之不暇。而又求誉乎。余方借轩而攘而有之之是恧。又敢借竹之贞与洁。而攘而有之乎。虽然。余亦欲因是以有复于诸生。竹可借也。贞与洁可借乎。况又进于贞与洁者乎。学道而无诸己也。则其将借之于雒于闽乎。学文而无诸己也。则其将借之于昌黎于庐陵乎。雒闽昌黎庐陵。犹不足借。况借于借者乎。况借于借而又未之能借者乎。余盖借于借而未之借者也。诸生其亦可以知所愧矣。而又奚云乎哉。除草说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8L 页
 天地之心。与人之心。其同耶。其不同耶。君子必荣尊富寿。小人反是。古诗书易圣人之书。多言之。其果然耶。而中世以下。负材奇辩之士。往往愤盈发呼。咎天理之不常。甚且谓天与人。好恶异趣。又岂然耶。彼其人。尝诵慕圣人。知足以弗畔。奈何卒为怪诡拂经之谈。务与圣人难哉。岂圣人之言。果诳人耶。彼岂其有所见者然耶。今之时。天下群共怨嫉。目为小人。而不可易者。谁欤。吾未之识也。吾心所诚服无疑。可以当君子者。谁欤。吾又未之多见也。其或荣尊富寿。其或反是。吾何从以卜天地之心哉。独见草之在吾庭者。其为吾所爱悦。欲其蕃者必难生。生则有风雨不时之患。及为牛马所践。婢子僮竖所亵。悴焉而不宁。其为吾所憎嫉而亟锄之者。一宿而视则复芽焉。不数日则挺然若怒。茁然若喜。若有所凭恃而王张肆大。快然无所畏也。是则谁使之然欤。将非天地之心之为之信欤。古圣人之言。果皆诳人欤。而中世以下。负材奇辩之士。其言贤于古圣人谓欤。抑吾尝读楚屈平之离骚。其人好草之芳馨者。辄比之君子。望其蕃而伤其悴。其情殷然不能已。岂非其性之近而有所取耶。盖孔子。亦尝叹猗兰云。然溯孔子以上周公。以至舜,皋陶。其所为诗歌及他所纪言语。未闻有芳草之类。为所好所取者。又何欤。岂古圣人君子之性。亦有然有不然耶。抑吾闻凤凰。鸟之瑞也。至可贵也。而周之三世。凤凰鸣而不去。卷阿之诗。以比蔼蔼之士。
天地之心。与人之心。其同耶。其不同耶。君子必荣尊富寿。小人反是。古诗书易圣人之书。多言之。其果然耶。而中世以下。负材奇辩之士。往往愤盈发呼。咎天理之不常。甚且谓天与人。好恶异趣。又岂然耶。彼其人。尝诵慕圣人。知足以弗畔。奈何卒为怪诡拂经之谈。务与圣人难哉。岂圣人之言。果诳人耶。彼岂其有所见者然耶。今之时。天下群共怨嫉。目为小人。而不可易者。谁欤。吾未之识也。吾心所诚服无疑。可以当君子者。谁欤。吾又未之多见也。其或荣尊富寿。其或反是。吾何从以卜天地之心哉。独见草之在吾庭者。其为吾所爱悦。欲其蕃者必难生。生则有风雨不时之患。及为牛马所践。婢子僮竖所亵。悴焉而不宁。其为吾所憎嫉而亟锄之者。一宿而视则复芽焉。不数日则挺然若怒。茁然若喜。若有所凭恃而王张肆大。快然无所畏也。是则谁使之然欤。将非天地之心之为之信欤。古圣人之言。果皆诳人欤。而中世以下。负材奇辩之士。其言贤于古圣人谓欤。抑吾尝读楚屈平之离骚。其人好草之芳馨者。辄比之君子。望其蕃而伤其悴。其情殷然不能已。岂非其性之近而有所取耶。盖孔子。亦尝叹猗兰云。然溯孔子以上周公。以至舜,皋陶。其所为诗歌及他所纪言语。未闻有芳草之类。为所好所取者。又何欤。岂古圣人君子之性。亦有然有不然耶。抑吾闻凤凰。鸟之瑞也。至可贵也。而周之三世。凤凰鸣而不去。卷阿之诗。以比蔼蔼之士。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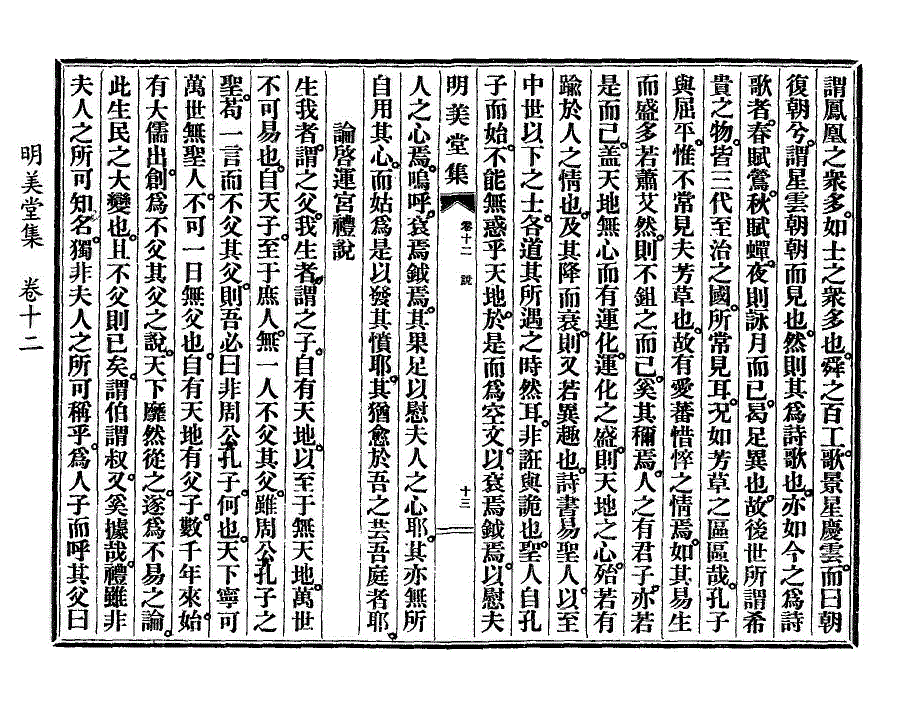 谓凤凰之众多。如士之众多也。舜之百工。歌景星庆云。而曰朝复朝兮。谓星云朝朝而见也。然则其为诗歌也。亦如今之为诗歌者。春赋莺。秋赋蝉。夜则咏月而已。曷足异也。故后世所谓希贵之物。皆三代至治之国。所常见耳。况如芳草之区区哉。孔子与屈平。惟不常见夫芳草也。故有爱蕃惜悴之情焉。如其易生而盛多若萧艾然。则不锄之而已。奚其称焉。人之有君子。亦若是而已。盖天地无心而有运化。运化之盛。则天地之心。殆若有踰于人之情也。及其降而衰。则又若异趣也。诗书易圣人。以至中世以下之士。各道其所遇之时然耳。非诳与诡也。圣人自孔子而始。不能无惑乎天地。于是而为空文。以衮焉钺焉。以慰夫人之心焉。呜呼。衮焉钺焉。其果足以慰夫人之心耶。其亦无所自用其心。而姑为是以发其愤耶。其犹愈于吾之芸吾庭者耶。
谓凤凰之众多。如士之众多也。舜之百工。歌景星庆云。而曰朝复朝兮。谓星云朝朝而见也。然则其为诗歌也。亦如今之为诗歌者。春赋莺。秋赋蝉。夜则咏月而已。曷足异也。故后世所谓希贵之物。皆三代至治之国。所常见耳。况如芳草之区区哉。孔子与屈平。惟不常见夫芳草也。故有爱蕃惜悴之情焉。如其易生而盛多若萧艾然。则不锄之而已。奚其称焉。人之有君子。亦若是而已。盖天地无心而有运化。运化之盛。则天地之心。殆若有踰于人之情也。及其降而衰。则又若异趣也。诗书易圣人。以至中世以下之士。各道其所遇之时然耳。非诳与诡也。圣人自孔子而始。不能无惑乎天地。于是而为空文。以衮焉钺焉。以慰夫人之心焉。呜呼。衮焉钺焉。其果足以慰夫人之心耶。其亦无所自用其心。而姑为是以发其愤耶。其犹愈于吾之芸吾庭者耶。论启运宫礼说
生我者。谓之父。我生者。谓之子。自有天地。以至于无天地。万世不可易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不父其父。虽周公,孔子之圣。苟一言而不父其父。则吾必曰非周公,孔子。何也。天下宁可万世无圣人。不可一日无父也。自有天地有父子。数千年来。始有大儒出。创为不父其父之说。天下靡然从之。遂为不易之论。此生民之大变也。且不父则已矣。谓伯谓叔。又奚据哉。礼虽非夫人之所可知名。独非夫人之所可称乎。为人子而呼其父曰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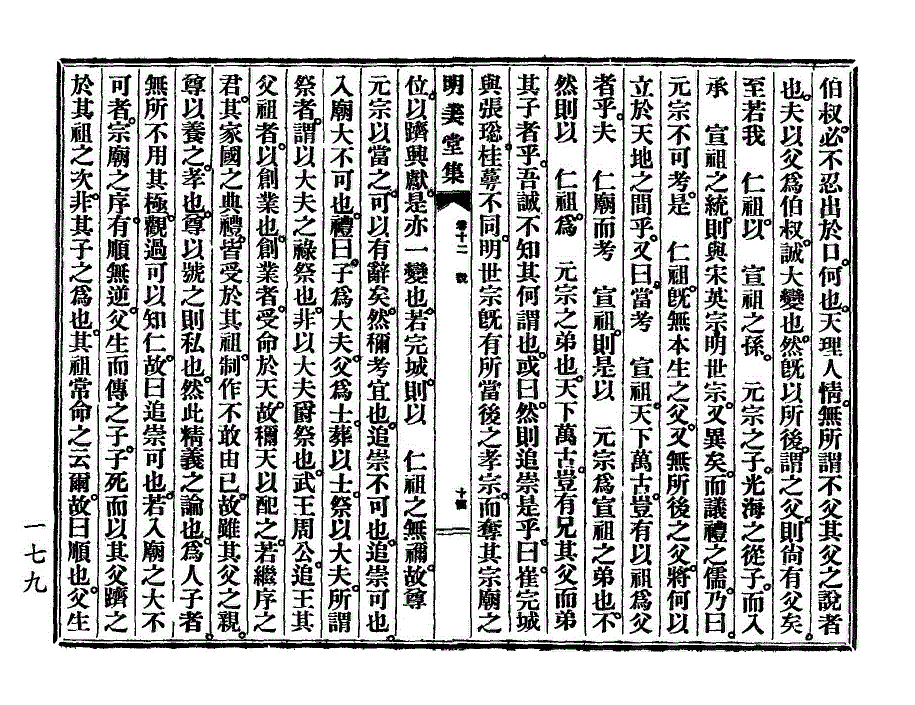 伯叔。必不忍出于口。何也。天理人情。无所谓不父其父之说者也。夫以父为伯叔。诚大变也。然既以所后。谓之父。则尚有父矣。至若我 仁祖。以 宣祖之孙。 元宗之子。光海之从子。而入承 宣祖之统。则与宋英宗,明世宗。又异矣。而议礼之儒。乃曰。元宗不可考。是 仁祖。既无本生之父。又无所后之父。将何以立于天地之间乎。又曰。当考 宣祖。天下万古。岂有以祖为父者乎。夫 仁庙而考 宣祖。则是以 元宗为宣祖之弟也。不然则以 仁祖。为 元宗之弟也。天下万古。岂有兄其父而弟其子者乎。吾诚不知其何谓也。或曰。然则追崇是乎。曰。崔完城与张𤥼。桂萼不同。明世宗既有所当后之孝宗。而夺其宗庙之位。以跻兴献。是亦一变也。若完城。则以 仁祖之无祢。故尊 元宗以当之。可以有辞矣。然称考宜也。追崇不可也。追崇可也。入庙大不可也。礼曰。子为大夫。父为士。葬以士。祭以大夫。所谓祭者。谓以大夫之禄祭也。非以大夫爵祭也。武王周公。追王其父祖者。以创业也。创业者。受命于天。故称天以配之。若继序之君。其家国之典礼。皆受于其祖。制作不敢由己。故虽其父之亲。尊以养之。孝也。尊以号之则私也。然此精义之论也。为人子者。无所不用其极。观过可以知仁。故曰追崇可也。若入庙之大不可者。宗庙之序。有顺无逆。父生而传之子。子死而以其父跻之于其祖之次。非其子之为也。其祖常命之云尔。故曰顺也。父生
伯叔。必不忍出于口。何也。天理人情。无所谓不父其父之说者也。夫以父为伯叔。诚大变也。然既以所后。谓之父。则尚有父矣。至若我 仁祖。以 宣祖之孙。 元宗之子。光海之从子。而入承 宣祖之统。则与宋英宗,明世宗。又异矣。而议礼之儒。乃曰。元宗不可考。是 仁祖。既无本生之父。又无所后之父。将何以立于天地之间乎。又曰。当考 宣祖。天下万古。岂有以祖为父者乎。夫 仁庙而考 宣祖。则是以 元宗为宣祖之弟也。不然则以 仁祖。为 元宗之弟也。天下万古。岂有兄其父而弟其子者乎。吾诚不知其何谓也。或曰。然则追崇是乎。曰。崔完城与张𤥼。桂萼不同。明世宗既有所当后之孝宗。而夺其宗庙之位。以跻兴献。是亦一变也。若完城。则以 仁祖之无祢。故尊 元宗以当之。可以有辞矣。然称考宜也。追崇不可也。追崇可也。入庙大不可也。礼曰。子为大夫。父为士。葬以士。祭以大夫。所谓祭者。谓以大夫之禄祭也。非以大夫爵祭也。武王周公。追王其父祖者。以创业也。创业者。受命于天。故称天以配之。若继序之君。其家国之典礼。皆受于其祖。制作不敢由己。故虽其父之亲。尊以养之。孝也。尊以号之则私也。然此精义之论也。为人子者。无所不用其极。观过可以知仁。故曰追崇可也。若入庙之大不可者。宗庙之序。有顺无逆。父生而传之子。子死而以其父跻之于其祖之次。非其子之为也。其祖常命之云尔。故曰顺也。父生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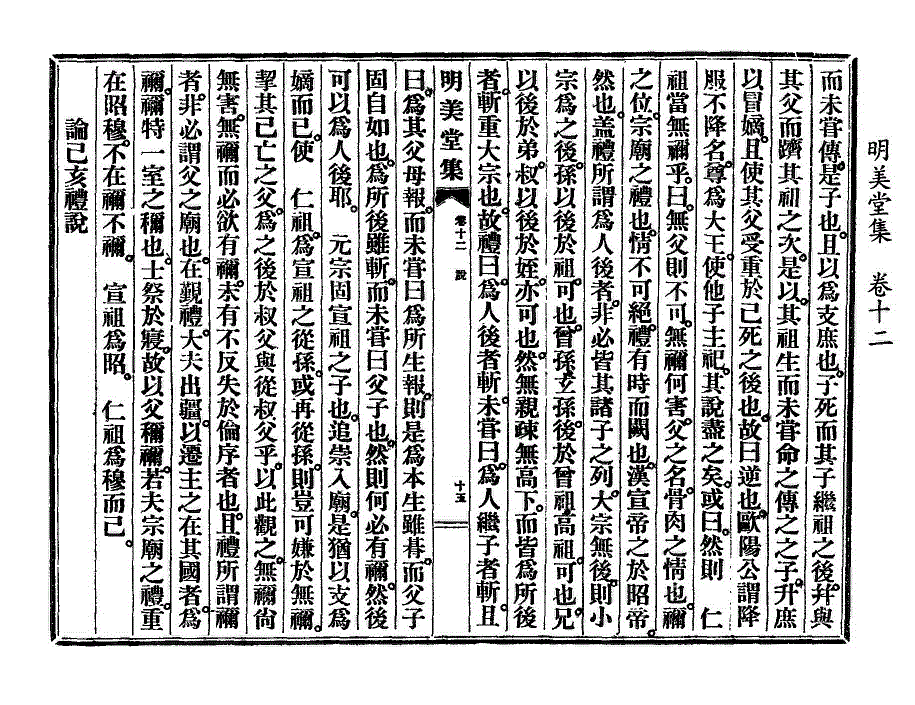 而未尝传。是子也。且以为支庶也。子死而其子继祖之后。并与其父而跻其祖之次。是以。其祖生而未尝命之传之之子。升庶以冒嫡。且使其父受重于已死之后也。故曰逆也。欧阳公谓降服不降名。尊为大王。使他子主祀。其说尽之矣。或曰。然则 仁祖当无祢乎。曰。无父则不可。无祢何害。父之名。骨肉之情也。祢之位。宗庙之礼也。情不可绝。礼有时而阙也。汉宣帝之于昭帝。然也。盖礼所谓为人后者。非必皆其诸子之列。大宗无后。则小宗为之后。孙以后于祖。可也。曾孙,玄孙。后于曾祖,高祖。可也。兄以后于弟。叔以后于侄。亦可也。然无亲疏无高下。而皆为所后者。斩重大宗也。故礼曰。为人后者斩。未尝曰。为人继子者斩。且曰。为其父母报。而未尝曰为所生报。则是为本生虽期。而父子固自如也。为所后虽斩。而未尝曰父子也。然则何必有祢。然后可以为人后耶。 元宗固宣祖之子也。追崇入庙。是犹以支为嫡而已。使 仁祖。为宣祖之从孙。或再从孙。则岂可嫌于无祢。挈其已亡之父。为之后于叔父与从叔父乎。以此观之。无祢尚无害。无祢而必欲有祢。未有不反失于伦序者也。且礼所谓祢者。非必谓父之庙也。在觐礼。大夫出疆。以迁主之在其国者。为祢。祢特一室之称也。士祭于寝。故以父称祢。若夫宗庙之礼。重在昭穆。不在祢不祢。 宣祖为昭。 仁祖为穆而已。
而未尝传。是子也。且以为支庶也。子死而其子继祖之后。并与其父而跻其祖之次。是以。其祖生而未尝命之传之之子。升庶以冒嫡。且使其父受重于已死之后也。故曰逆也。欧阳公谓降服不降名。尊为大王。使他子主祀。其说尽之矣。或曰。然则 仁祖当无祢乎。曰。无父则不可。无祢何害。父之名。骨肉之情也。祢之位。宗庙之礼也。情不可绝。礼有时而阙也。汉宣帝之于昭帝。然也。盖礼所谓为人后者。非必皆其诸子之列。大宗无后。则小宗为之后。孙以后于祖。可也。曾孙,玄孙。后于曾祖,高祖。可也。兄以后于弟。叔以后于侄。亦可也。然无亲疏无高下。而皆为所后者。斩重大宗也。故礼曰。为人后者斩。未尝曰。为人继子者斩。且曰。为其父母报。而未尝曰为所生报。则是为本生虽期。而父子固自如也。为所后虽斩。而未尝曰父子也。然则何必有祢。然后可以为人后耶。 元宗固宣祖之子也。追崇入庙。是犹以支为嫡而已。使 仁祖。为宣祖之从孙。或再从孙。则岂可嫌于无祢。挈其已亡之父。为之后于叔父与从叔父乎。以此观之。无祢尚无害。无祢而必欲有祢。未有不反失于伦序者也。且礼所谓祢者。非必谓父之庙也。在觐礼。大夫出疆。以迁主之在其国者。为祢。祢特一室之称也。士祭于寝。故以父称祢。若夫宗庙之礼。重在昭穆。不在祢不祢。 宣祖为昭。 仁祖为穆而已。论己亥礼说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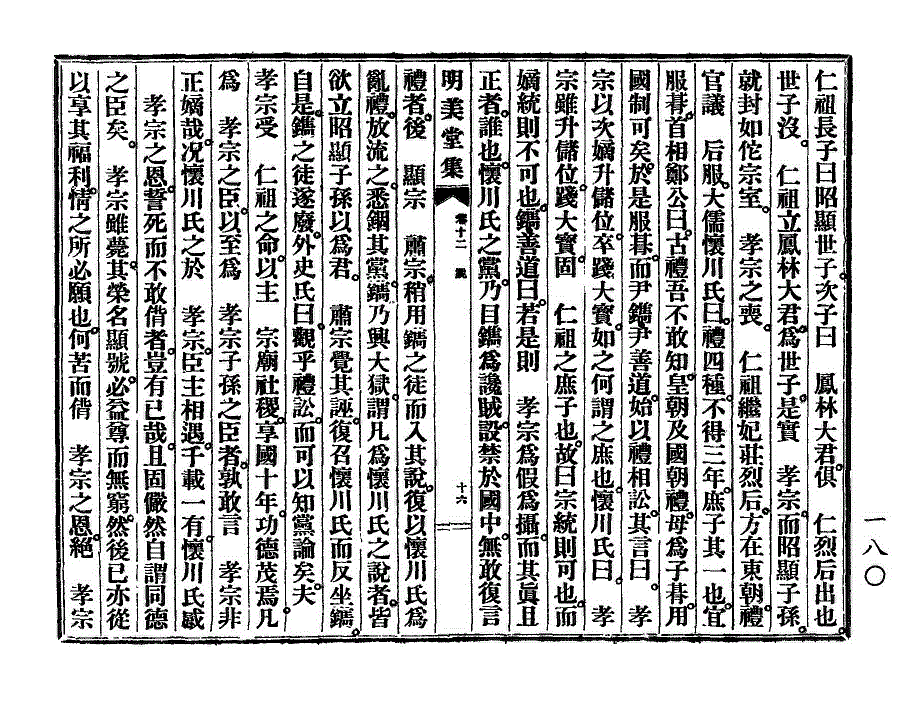 仁祖长子曰昭显世子。次子曰 凤林大君。俱 仁烈后出也。世子没。 仁祖立凤林大君。为世子。是实 孝宗。而昭显子孙。就封如佗宗室。 孝宗之丧。 仁祖继妃庄烈后。方在东朝。礼官议 后服。大儒怀川氏曰。礼四种。不得三年。庶子其一也。宜服期。首相郑公曰。古礼吾不敢知。皇朝及国朝礼。母为子期。用国制可矣。于是服期。而尹鑴,尹善道。始以礼相讼。其言曰。 孝宗以次嫡升储位。卒践大宝。如之何谓之庶也。怀川氏曰。 孝宗虽升储位。践大宝。固 仁祖之庶子也。故曰宗统则可也。而嫡统则不可也。鑴,善道曰。若是则 孝宗为假为摄。而其真且正者。谁也。怀川氏之党。乃目鑴为谗贼。设禁于国中。无敢复言礼者。后 显宗 肃宗。稍用鑴之徒而入其说。复以怀川氏为乱礼。放流之。悉锢其党。鑴乃兴大狱。谓凡为怀川氏之说者。皆欲立昭显子孙以为君。 肃宗觉其诬。复召怀川氏而反坐鑴。自是。鑴之徒遂废。外史氏曰。观乎礼讼。而可以知党论矣。夫 孝宗受 仁祖之命。以主 宗庙社稷。享国十年。功德茂焉。凡为 孝宗之臣。以至为 孝宗子孙之臣者。孰敢言 孝宗非正嫡哉。况怀川氏之于 孝宗。臣主相遇。千载一有。怀川氏感 孝宗之恩。誓死而不敢背者。岂有已哉。且固俨然自谓同德之臣矣。 孝宗虽薨。其荣名显号。必益尊而无穷。然后已亦从以享其福利。情之所必愿也。何苦而背 孝宗之恩。绝 孝宗
仁祖长子曰昭显世子。次子曰 凤林大君。俱 仁烈后出也。世子没。 仁祖立凤林大君。为世子。是实 孝宗。而昭显子孙。就封如佗宗室。 孝宗之丧。 仁祖继妃庄烈后。方在东朝。礼官议 后服。大儒怀川氏曰。礼四种。不得三年。庶子其一也。宜服期。首相郑公曰。古礼吾不敢知。皇朝及国朝礼。母为子期。用国制可矣。于是服期。而尹鑴,尹善道。始以礼相讼。其言曰。 孝宗以次嫡升储位。卒践大宝。如之何谓之庶也。怀川氏曰。 孝宗虽升储位。践大宝。固 仁祖之庶子也。故曰宗统则可也。而嫡统则不可也。鑴,善道曰。若是则 孝宗为假为摄。而其真且正者。谁也。怀川氏之党。乃目鑴为谗贼。设禁于国中。无敢复言礼者。后 显宗 肃宗。稍用鑴之徒而入其说。复以怀川氏为乱礼。放流之。悉锢其党。鑴乃兴大狱。谓凡为怀川氏之说者。皆欲立昭显子孙以为君。 肃宗觉其诬。复召怀川氏而反坐鑴。自是。鑴之徒遂废。外史氏曰。观乎礼讼。而可以知党论矣。夫 孝宗受 仁祖之命。以主 宗庙社稷。享国十年。功德茂焉。凡为 孝宗之臣。以至为 孝宗子孙之臣者。孰敢言 孝宗非正嫡哉。况怀川氏之于 孝宗。臣主相遇。千载一有。怀川氏感 孝宗之恩。誓死而不敢背者。岂有已哉。且固俨然自谓同德之臣矣。 孝宗虽薨。其荣名显号。必益尊而无穷。然后已亦从以享其福利。情之所必愿也。何苦而背 孝宗之恩。绝 孝宗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1H 页
 之统。使 孝宗之子孙。不安于天位。而自附于所不知之何人。违情拂理。以蹈天下之大逆哉。此妇孺之所可辨也。而鑴,善道倡之。其徒之号有识者皆和之。真以怀川氏为叛 孝宗也。自古谗人之罔极。未有甚于此者。可不痛乎。抑所恶于谗人者。以其所谗。必君子也。所爱于君子者。以其言与事必是也。其言与事必是。则虽喑昧于一时。必彰明较著于天下万世。虽无人主之令。与其党与之助。而后之论者胥归焉。夫鑴,善道。诚谗人也。则怀川氏必君子也。其言必是也。是则余之所不敢质也。夫礼固非夫人之所知也。若夫贵嫡而贱庶。夫人之所知也。有人于此。实庶也。吾犹不斥言其庶。为其贱之也。况非庶而斥曰庶可乎。于敌犹不可。况于至尊乎。为怀川氏之说者。则曰凡第二子。虽非妾出。皆庶也。古礼之不知。乌知嫡庶。夫第二子之谓庶。非僻书也。读礼记者。皆知之矣。古之知礼者。于历代典章。无所不究。于天下之义理。无所不通。其所知。常出于众人之外。而其所行。常就乎众人之所安。后之知礼者。不过知众人之所知。而尝欲行众人之所不安。此礼之所以失其本也。夫三年与期。不必争也。庶与嫡。又不必卞也。惟所谓第二子之说。何从而发哉。 孝宗之于 仁祖。为第二子而非长子。则亦夫人之所知也。然当 仁祖之舍孙而立 孝宗也。臣下争之曰。此第二子而非长子云尔。则其言诚宜也。 孝宗既立。享国十年而薨。 嗣子
之统。使 孝宗之子孙。不安于天位。而自附于所不知之何人。违情拂理。以蹈天下之大逆哉。此妇孺之所可辨也。而鑴,善道倡之。其徒之号有识者皆和之。真以怀川氏为叛 孝宗也。自古谗人之罔极。未有甚于此者。可不痛乎。抑所恶于谗人者。以其所谗。必君子也。所爱于君子者。以其言与事必是也。其言与事必是。则虽喑昧于一时。必彰明较著于天下万世。虽无人主之令。与其党与之助。而后之论者胥归焉。夫鑴,善道。诚谗人也。则怀川氏必君子也。其言必是也。是则余之所不敢质也。夫礼固非夫人之所知也。若夫贵嫡而贱庶。夫人之所知也。有人于此。实庶也。吾犹不斥言其庶。为其贱之也。况非庶而斥曰庶可乎。于敌犹不可。况于至尊乎。为怀川氏之说者。则曰凡第二子。虽非妾出。皆庶也。古礼之不知。乌知嫡庶。夫第二子之谓庶。非僻书也。读礼记者。皆知之矣。古之知礼者。于历代典章。无所不究。于天下之义理。无所不通。其所知。常出于众人之外。而其所行。常就乎众人之所安。后之知礼者。不过知众人之所知。而尝欲行众人之所不安。此礼之所以失其本也。夫三年与期。不必争也。庶与嫡。又不必卞也。惟所谓第二子之说。何从而发哉。 孝宗之于 仁祖。为第二子而非长子。则亦夫人之所知也。然当 仁祖之舍孙而立 孝宗也。臣下争之曰。此第二子而非长子云尔。则其言诚宜也。 孝宗既立。享国十年而薨。 嗣子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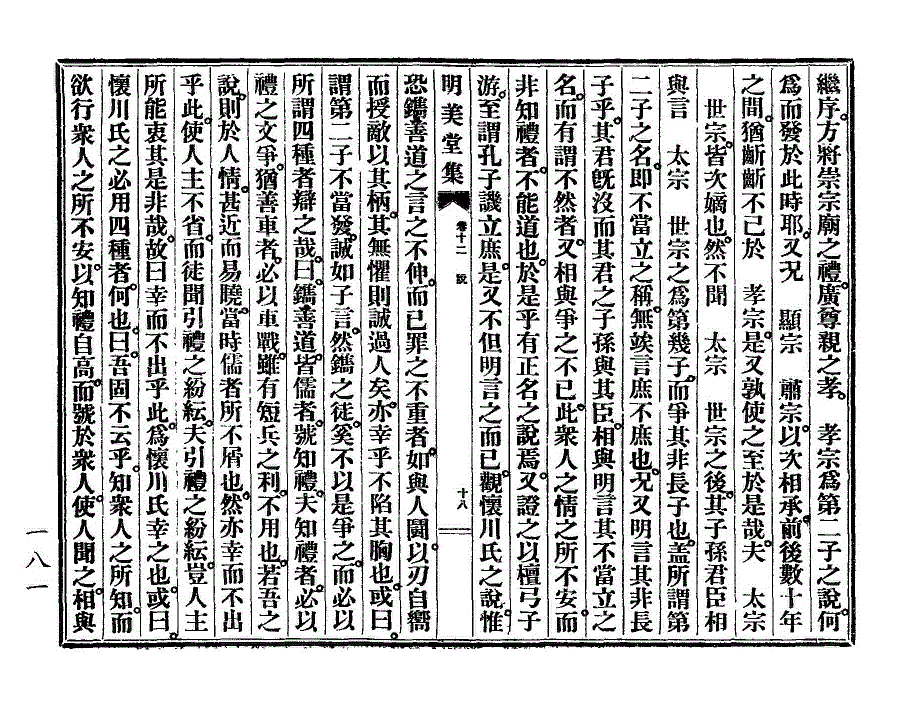 继序。方将崇宗庙之礼。广尊亲之孝。 孝宗为第二子之说。何为而发于此时耶。又况 显宗 肃宗。以次相承。前后数十年之间。犹龂龂不已于 孝宗。是又孰使之至于是哉。夫 太宗 世宗。皆次嫡也。然不闻 太宗 世宗之后。其子孙君臣相与言 太宗 世宗之为第几子。而争其非长子也。盖所谓第二子之名。即不当立之称。无俟言庶不庶也。况又明言其非长子乎。其君既没而其君之子孙与其臣。相与明言其不当立之名。而有谓不然者。又相与争之不已。此众人之情之所不安。而非知礼者。不能道也。于是乎有正名之说焉。又證之以檀弓子游。至谓孔子讥立庶。是又不但明言之而已。观怀川氏之说。惟恐鑴,善道之言之不伸。而己罪之不重者。如与人斗。以刃自向而授敌以其柄。其无惧则诚过人矣。亦幸乎不陷其胸也。或曰。谓第二子不当发。诚如子言。然鑴之徒。奚不以是争之。而必以所谓四种者辩之哉。曰。鑴,善道。皆儒者。号知礼。夫知礼者。必以礼之文争。犹善车者。必以车战。虽有短兵之利。不用也。若吾之说。则于人情。甚近而易晓。当时儒者所不屑也。然亦幸而不出乎此。使人主不省。而徒闻引礼之纷纭。夫引礼之纷纭。岂人主所能衷其是非哉。故曰幸而不出乎此。为怀川氏幸之也。或曰。怀川氏之必用四种者。何也。曰。吾固不云乎。知众人之所知。而欲行众人之所不安。以知礼自高。而号于众人。使人闻之。相与
继序。方将崇宗庙之礼。广尊亲之孝。 孝宗为第二子之说。何为而发于此时耶。又况 显宗 肃宗。以次相承。前后数十年之间。犹龂龂不已于 孝宗。是又孰使之至于是哉。夫 太宗 世宗。皆次嫡也。然不闻 太宗 世宗之后。其子孙君臣相与言 太宗 世宗之为第几子。而争其非长子也。盖所谓第二子之名。即不当立之称。无俟言庶不庶也。况又明言其非长子乎。其君既没而其君之子孙与其臣。相与明言其不当立之名。而有谓不然者。又相与争之不已。此众人之情之所不安。而非知礼者。不能道也。于是乎有正名之说焉。又證之以檀弓子游。至谓孔子讥立庶。是又不但明言之而已。观怀川氏之说。惟恐鑴,善道之言之不伸。而己罪之不重者。如与人斗。以刃自向而授敌以其柄。其无惧则诚过人矣。亦幸乎不陷其胸也。或曰。谓第二子不当发。诚如子言。然鑴之徒。奚不以是争之。而必以所谓四种者辩之哉。曰。鑴,善道。皆儒者。号知礼。夫知礼者。必以礼之文争。犹善车者。必以车战。虽有短兵之利。不用也。若吾之说。则于人情。甚近而易晓。当时儒者所不屑也。然亦幸而不出乎此。使人主不省。而徒闻引礼之纷纭。夫引礼之纷纭。岂人主所能衷其是非哉。故曰幸而不出乎此。为怀川氏幸之也。或曰。怀川氏之必用四种者。何也。曰。吾固不云乎。知众人之所知。而欲行众人之所不安。以知礼自高。而号于众人。使人闻之。相与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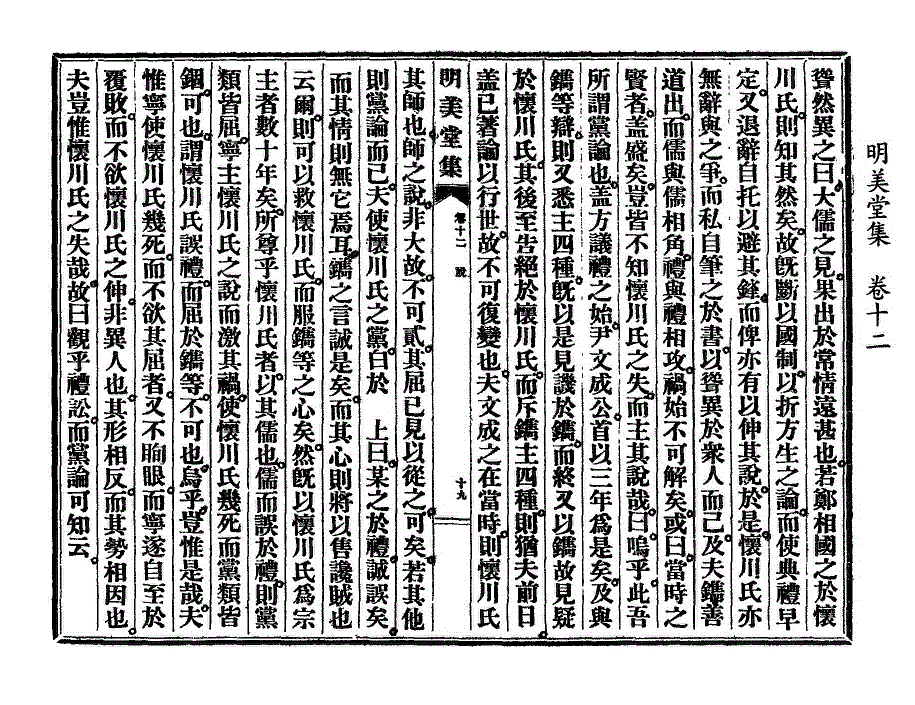 耸然异之曰。大儒之见。果出于常情远甚也。若郑相国之于怀川氏。则知其然矣。故既断以国制。以折方生之论。而使典礼早定。又退辞自托以避其锋。而俾亦有以伸其说。于是。怀川氏亦无辞与之争。而私自笔之于书。以耸异于众人而已。及夫鑴,善道出。而儒与儒相角。礼与礼相攻。祸始不可解矣。或曰。当时之贤者。盖盛矣。岂皆不知怀川氏之失。而主其说哉。曰。呜乎。此吾所谓党论也。盖方议礼之始。尹文成公。首以三年为是矣。及与鑴等辩。则又悉主四种。既以是见讥于鑴。而终又以鑴故见疑于怀川氏。其后至告绝于怀川氏。而斥鑴主四种。则犹夫前日。盖已著论以行世。故不可复变也。夫文成之在当时。则怀川氏其师也。师之说。非大故。不可贰。其屈己见以从之。可矣。若其他则党论而已。夫使怀川氏之党。白于 上曰。某之于礼。诚误矣。而其情则无它焉耳。鑴之言诚是矣。而其心则将以售谗贼也云尔。则可以救怀川氏。而服鑴等之心矣。然既以怀川氏为宗主者数十年矣。所尊乎怀川氏者。以其儒也。儒而误于礼。则党类皆屈。宁主怀川氏之说而激其祸。使怀川氏几死而党类皆锢。可也。谓怀川氏误礼。而屈于鑴等。不可也。乌乎。岂惟是哉。夫惟宁使怀川氏几死。而不欲其屈者。又不眴眼。而宁遂自至于覆败。而不欲怀川氏之伸。非异人也。其形相反。而其势相因也。夫岂惟怀川氏之失哉。故曰观乎礼讼。而党论可知云。
耸然异之曰。大儒之见。果出于常情远甚也。若郑相国之于怀川氏。则知其然矣。故既断以国制。以折方生之论。而使典礼早定。又退辞自托以避其锋。而俾亦有以伸其说。于是。怀川氏亦无辞与之争。而私自笔之于书。以耸异于众人而已。及夫鑴,善道出。而儒与儒相角。礼与礼相攻。祸始不可解矣。或曰。当时之贤者。盖盛矣。岂皆不知怀川氏之失。而主其说哉。曰。呜乎。此吾所谓党论也。盖方议礼之始。尹文成公。首以三年为是矣。及与鑴等辩。则又悉主四种。既以是见讥于鑴。而终又以鑴故见疑于怀川氏。其后至告绝于怀川氏。而斥鑴主四种。则犹夫前日。盖已著论以行世。故不可复变也。夫文成之在当时。则怀川氏其师也。师之说。非大故。不可贰。其屈己见以从之。可矣。若其他则党论而已。夫使怀川氏之党。白于 上曰。某之于礼。诚误矣。而其情则无它焉耳。鑴之言诚是矣。而其心则将以售谗贼也云尔。则可以救怀川氏。而服鑴等之心矣。然既以怀川氏为宗主者数十年矣。所尊乎怀川氏者。以其儒也。儒而误于礼。则党类皆屈。宁主怀川氏之说而激其祸。使怀川氏几死而党类皆锢。可也。谓怀川氏误礼。而屈于鑴等。不可也。乌乎。岂惟是哉。夫惟宁使怀川氏几死。而不欲其屈者。又不眴眼。而宁遂自至于覆败。而不欲怀川氏之伸。非异人也。其形相反。而其势相因也。夫岂惟怀川氏之失哉。故曰观乎礼讼。而党论可知云。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2L 页
 易圈说(出读易随记)
易圈说(出读易随记)易之画二。奇偶也。易之位三。上中下也。二画乘乎三位。而其象为四。三阳也。三阴也。一阳二阴也。一阴二阳也。所谓四营而成易也。一画逆顺。具有三位。三画之位十八。所谓十有八变。而成卦也。四象之中。三阳三阴。画纯而位定。故惟成乾坤。一阳二阴。画杂而位移。故阳下成震。阳中成坎。阳上成艮。一阴二阳。亦然。故成巽成离成兑。所谓八卦而小成也。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而六十四卦。备矣。上古圣人作易之本。盖弗过乎是矣。汉尚纬学。宋取道家。皆以河图论易。专主对待。故有排张垛叠之势。如所谓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有位而无名。又如剥变晋。晋变大有。竟亦莫晓其义。苟能扫除对待之象。而独观夫作易之本。则一理流行。而众妙历然。朱子所云。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者。是也。然对待既有图。则流行不应无图。对待须方。流行须圆。诸家圆图。皆因以重之以后之流行。而非八卦小成以前之流行也。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而知。爻之德。杂而贡。蓍今不可得见。然图卦不如图爻。爻虽卦中之爻。而卦本以爻而画。爻即画也。蓍之所取象也。易之最先也。今图爻而用图卦之圆法。则卦在其中。而蓍之德可见矣。故三阳之圈。得乾六。三阴之圈。得坤六。一阳二阴之圈。得震等三卦各二。一阴二阳之圈。得巽等三卦各二。因而重之。则一阳五阴之圈。得复等六卦各二。一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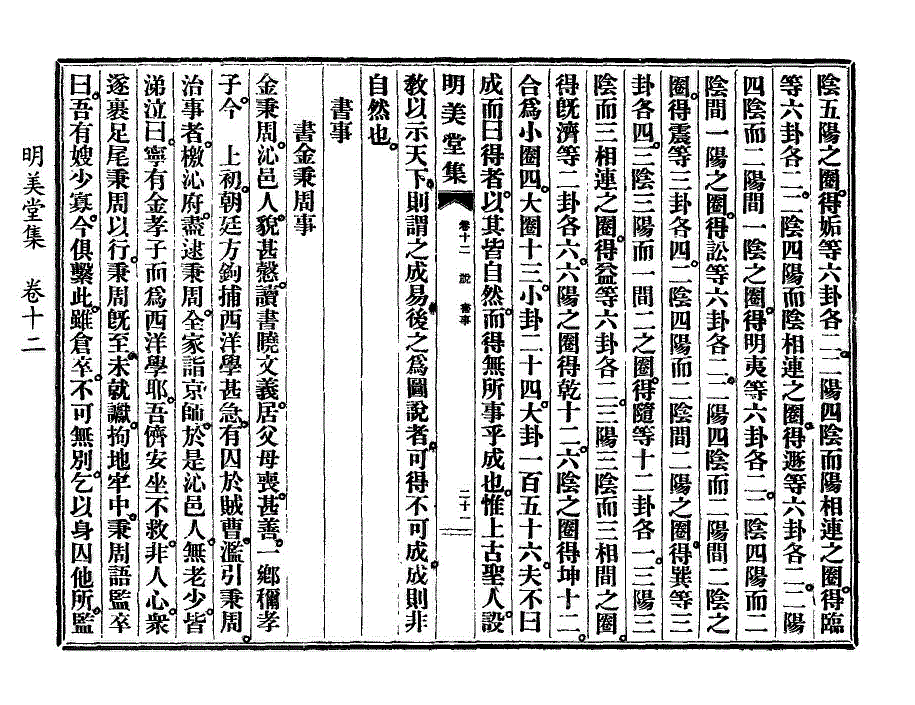 阴五阳之圈。得姤等六卦各二。二阳四阴而阳相连之圈。得临等六卦各二。二阴四阳而阴相连之圈。得遁等六卦各二。二阳四阴而二阳间一阴之圈。得明夷等六卦各二。二阴四阳而二阴间一阳之圈。得讼等六卦各二。二阳四阴而二阳间二阴之圈。得震等三卦各四。二阴四阳而二阴间二阳之圈。得巽等三卦各四。三阴三阳而一间二之圈。得随等十二卦各一。三阳三阴而三相连之圈。得益等六卦各二。三阳三阴而三相间之圈。得既济等二卦各六。六阳之圈得乾十二。六阴之圈得坤十二。合为小圈四。大圈十三。小卦二十四。大卦一百五十六。夫不曰成而曰得者。以其皆自然。而得无所事乎成也。惟上古圣人。设教以示天下。则谓之成易。后之为图说者。可得不可成。成则非自然也。
阴五阳之圈。得姤等六卦各二。二阳四阴而阳相连之圈。得临等六卦各二。二阴四阳而阴相连之圈。得遁等六卦各二。二阳四阴而二阳间一阴之圈。得明夷等六卦各二。二阴四阳而二阴间一阳之圈。得讼等六卦各二。二阳四阴而二阳间二阴之圈。得震等三卦各四。二阴四阳而二阴间二阳之圈。得巽等三卦各四。三阴三阳而一间二之圈。得随等十二卦各一。三阳三阴而三相连之圈。得益等六卦各二。三阳三阴而三相间之圈。得既济等二卦各六。六阳之圈得乾十二。六阴之圈得坤十二。合为小圈四。大圈十三。小卦二十四。大卦一百五十六。夫不曰成而曰得者。以其皆自然。而得无所事乎成也。惟上古圣人。设教以示天下。则谓之成易。后之为图说者。可得不可成。成则非自然也。明美堂集卷十二(全州李建昌凤朝 著)
书事
书金秉周事
金秉周。沁邑人。貌甚悫。读书晓文义。居父母丧。甚善。一乡称孝子。今 上初。朝廷方钩捕西洋学甚急。有囚于贼曹。滥引秉周。治事者。檄沁府。尽逮秉周。全家诣京师。于是沁邑人。无老少。皆涕泣曰。宁有金孝子而为西洋学耶。吾侪安坐不救。非人心。众遂裹足尾秉周以行。秉周既至。未就谳。拘地牢中。秉周语监卒曰。吾有嫂少寡。今俱系此。虽仓卒。不可无别。乞以身囚他所。监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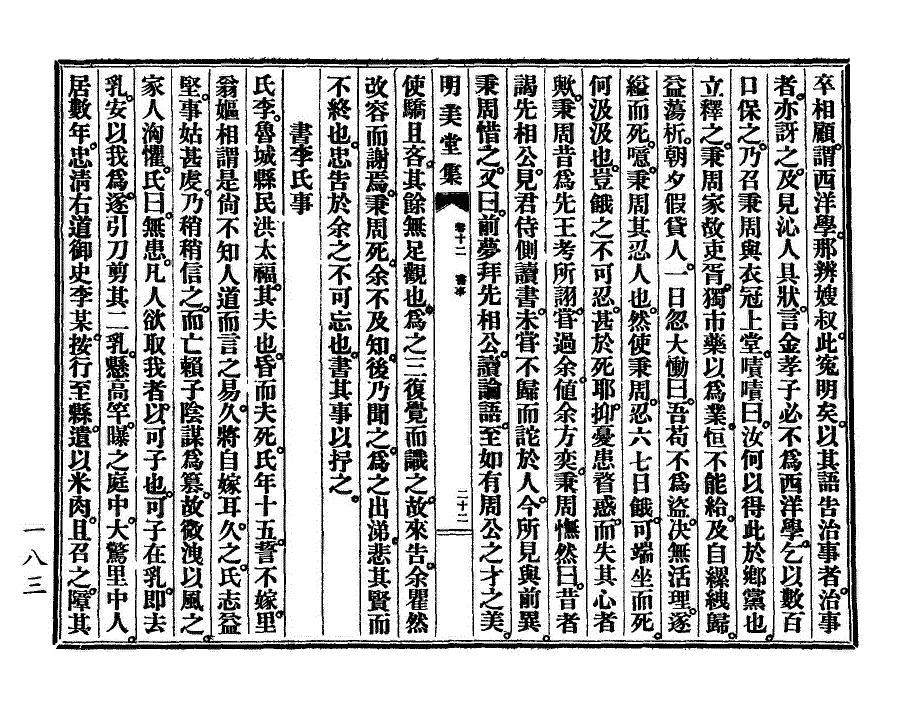 卒相顾。谓西洋学。那辨嫂叔。此冤明矣。以其语告治事者。治事者。亦讶之。及见沁人具状。言金孝子必不为西洋学。乞以数百口保之。乃召秉周与衣冠上堂。啧啧曰。汝何以得此于乡党也。立释之。秉周家故吏胥。独市药以为业。恒不能给。及自缧绁归。益荡析。朝夕假贷人。一日忽大恸曰。吾苟不为盗。决无活理。遂缢而死。噫。秉周其忍人也。然使秉周。忍六七日饿。可端坐而死。何汲汲也。岂饿之不可忍。甚于死耶。抑忧患瞀惑。而失其心者欤。秉周昔为先王考所诩。尝过余。值余方奕。秉周怃然曰。昔者谒先相公。见君侍侧读书。未尝不归而詑于人。今所见与前异。秉周惜之。又曰。前梦拜先相公。读论语。至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无足观也。为之三复觉而识之。故来告。余瞿然改容而谢焉。秉周死。余不及知。后乃闻之。为之出涕。悲其贤而不终也。忠告于余之不可忘也。书其事以抒之。
卒相顾。谓西洋学。那辨嫂叔。此冤明矣。以其语告治事者。治事者。亦讶之。及见沁人具状。言金孝子必不为西洋学。乞以数百口保之。乃召秉周与衣冠上堂。啧啧曰。汝何以得此于乡党也。立释之。秉周家故吏胥。独市药以为业。恒不能给。及自缧绁归。益荡析。朝夕假贷人。一日忽大恸曰。吾苟不为盗。决无活理。遂缢而死。噫。秉周其忍人也。然使秉周。忍六七日饿。可端坐而死。何汲汲也。岂饿之不可忍。甚于死耶。抑忧患瞀惑。而失其心者欤。秉周昔为先王考所诩。尝过余。值余方奕。秉周怃然曰。昔者谒先相公。见君侍侧读书。未尝不归而詑于人。今所见与前异。秉周惜之。又曰。前梦拜先相公。读论语。至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无足观也。为之三复觉而识之。故来告。余瞿然改容而谢焉。秉周死。余不及知。后乃闻之。为之出涕。悲其贤而不终也。忠告于余之不可忘也。书其事以抒之。书李氏事
氏李。鲁城县民洪太福。其夫也。昏而夫死。氏年十五。誓不嫁。里翁妪相谓是尚不知人道而言之易。久将自嫁耳。久之。氏志益坚。事姑甚虔。乃稍稍信之。而亡赖子阴谋为篡。故微泄以风之。家人汹惧。氏曰。无患。凡人欲取我者。以可子也。可子在乳。即去乳。安以我为。遂引刀剪其二乳。悬高竿。曝之庭中。大惊里中人。居数年。忠清右道御史李某。按行至县。遗以米肉。且召之。障其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4H 页
 面以帏。而见其乳。如未始有乳者。其姑曰。剪之夕。创则已。无苦云。
面以帏。而见其乳。如未始有乳者。其姑曰。剪之夕。创则已。无苦云。赞曰。昔夏侯令女。夫蚤死。恐家嫁已。乃断发为誓。其后复截两耳。及夫家夷灭。归父家。复断其鼻。古烈女戕身以完节。未有烈于令女。然彼其数数然者。岂得已哉。若李氏之剪乳。烈且智矣。然令女家世贵显。而氏之母。尝为人婢云。乌呼。不尤难哉。
书新孝子事
宝城郡大谷里。有李姓人。本贯庆州。流寓不振。尚以士族行。为人椎鲁不识字。与母兄析居。能力田以自温。兄窭甚。有时饥饿其母。而弟若罔闻。里中目之为不孝子。今年三十馀矣。夏四月。 制书下。令外道监司。修明乡约。劝孝悌。禁邪辟。籍民之善恶而奖抶之。郡守奉 制书。用古读法礼。布谕大小人民。此人于稠众中。闻所谕意。頫首悯默良久。径趋至母家。跽谢其兄曰。弟昏不孝不悌。罪不可活。幸以母与兄之爱。许我改乎。则请奉私赀三之二。以助兄事母。又曰。弟心欲养母于弟之家。然兄长子也。弟不敢干。母与兄大惊叹。退则具籍其田产归之兄。而又以其私。为母具食物。每五日一适市。买鲜鱼以进。自是里中呼此人为新孝子。乡约长以会之日。召而与之酒。书其名于善籍。且问何以能改之速也。此人不能答。頫首而已。李生秉玮。为余道如此。
明美堂集卷十二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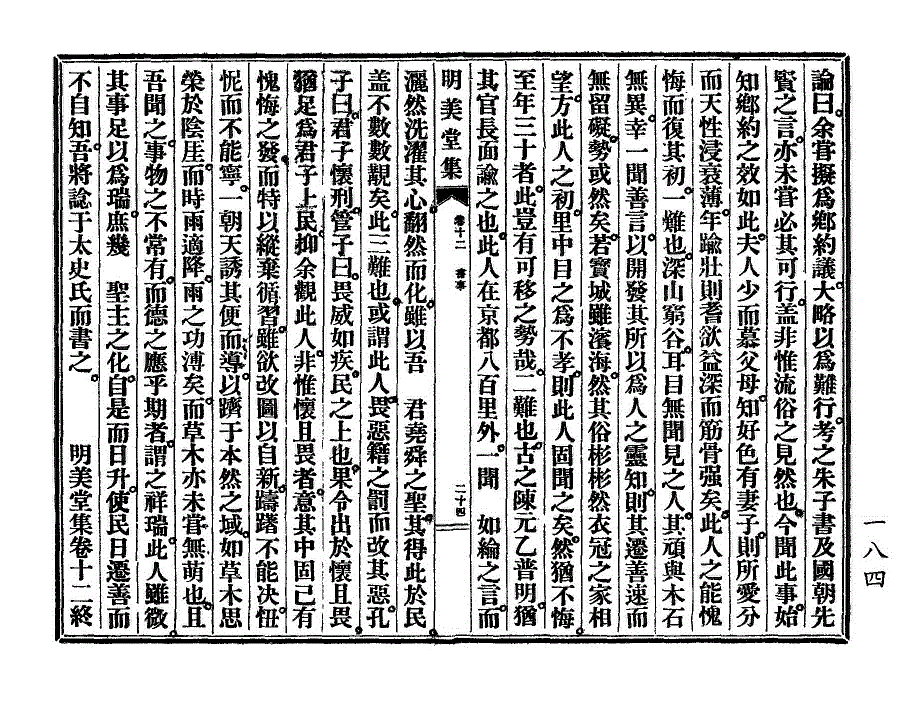 论曰。余尝拟为乡约议。大略以为难行。考之朱子书及国朝先贤之言。亦未尝必其可行。盖非惟流俗之见然也。今闻此事。始知乡约之效如此。夫人少而慕父母。知好色有妻子。则所爱分而天性浸衰薄。年踰壮则耆欲益深而筋骨强矣。此人之能愧悔而复其初。一难也。深山穷谷。耳目无闻见之人。其顽与木石无异。幸一闻善言。以开发其所以为人之灵知。则其迁善速而无留碍。势或然矣。若宝城虽滨海。然其俗彬彬然衣冠之家相望。方此人之初。里中目之为不孝。则此人固闻之矣。然犹不悔。至年三十者。此岂有可移之势哉。二难也。古之陈元乙普明。犹其官长面谕之也。此人在京都八百里外。一闻 如纶之言。而洒然洗濯其心。翻然而化。虽以吾 君尧舜之圣。其得此于民。盖不数数觏矣。此三难也。或谓此人。畏恶籍之罚而改其恶。孔子曰。君子怀刑。管子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果令出于怀且畏。犹足为君子上民。抑余观此人。非惟怀且畏者。意其中固己有愧悔之发。而特以纵弃循习。虽欲改图以自新。踌躇不能决。忸怩而不能宁。一朝天诱其便而导。以跻于本然之域。如草木思荣于阴厓。而时雨适降。雨之功溥矣。而草木亦未尝无萌也。且吾闻之。事物之不常有。而德之应乎期者。谓之祥瑞。此人虽微。其事足以为瑞。庶几 圣主之化。自是而日升。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吾将谂于太史氏而书之。
论曰。余尝拟为乡约议。大略以为难行。考之朱子书及国朝先贤之言。亦未尝必其可行。盖非惟流俗之见然也。今闻此事。始知乡约之效如此。夫人少而慕父母。知好色有妻子。则所爱分而天性浸衰薄。年踰壮则耆欲益深而筋骨强矣。此人之能愧悔而复其初。一难也。深山穷谷。耳目无闻见之人。其顽与木石无异。幸一闻善言。以开发其所以为人之灵知。则其迁善速而无留碍。势或然矣。若宝城虽滨海。然其俗彬彬然衣冠之家相望。方此人之初。里中目之为不孝。则此人固闻之矣。然犹不悔。至年三十者。此岂有可移之势哉。二难也。古之陈元乙普明。犹其官长面谕之也。此人在京都八百里外。一闻 如纶之言。而洒然洗濯其心。翻然而化。虽以吾 君尧舜之圣。其得此于民。盖不数数觏矣。此三难也。或谓此人。畏恶籍之罚而改其恶。孔子曰。君子怀刑。管子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果令出于怀且畏。犹足为君子上民。抑余观此人。非惟怀且畏者。意其中固己有愧悔之发。而特以纵弃循习。虽欲改图以自新。踌躇不能决。忸怩而不能宁。一朝天诱其便而导。以跻于本然之域。如草木思荣于阴厓。而时雨适降。雨之功溥矣。而草木亦未尝无萌也。且吾闻之。事物之不常有。而德之应乎期者。谓之祥瑞。此人虽微。其事足以为瑞。庶几 圣主之化。自是而日升。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吾将谂于太史氏而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