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x 页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记
记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0H 页
 一松亭记(己亥)
一松亭记(己亥)京城之东巷。有亭曰一松。其松也在室东隙地。自根而上。四五屈折然后。布枝作侧盖状。昼以障日。宵以迎月。微风之来。泠然出笙竽音。即大风雨则如三军赴敌。铁马崩腾。其可畏哉。然以其地之湫隘也。枝之可丈袤者止于尺。干之可拱大者止于把。气之不能舒者横出。为拥肿郁郁然。如九尺丈夫匍匐瓮牖下。又如怀才抱器之人。不能得高位。而屈首帖耳。趋走人之下者。余谓亭之主人。请子巍其门大其宇拓其庭。无为松忧。否则舍此而去之于百亩之宫千武之园。奇花异草。灵林嘉木。纷纷郁郁。无之不足。亦何独取此松为。主人笑曰。以吾不才。厕迹于朝。旅进旅退。无一建立。得有此居。乃其幸也。夫此居也。吾方且以为已美。矧敢望其加。余为之谢曰。善哉言乎。夫志于大者。小物不能累。安于约者。所及必博。姑以子之先祖文忠公言之。出入将相三十年。家无担石。垣屋不治。清俭贫薄如此。而其泽及生民。功垂社稷。顾何如哉。子能推子之言。则他日建立。其将庶几乎其先德矣。可不钦诸。遂索酒饮松下。因以记松之美。
黄州月波楼重修记(代○癸卯)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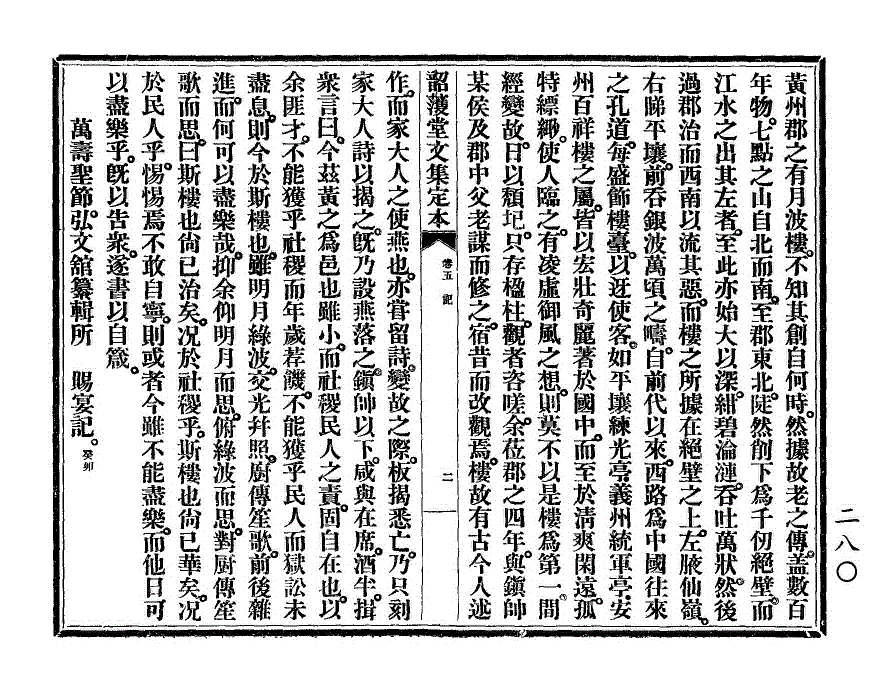 黄州郡之有月波楼。不知其创自何时。然据故老之传。盖数百年物。七点之山自北而南。至郡东北。陡然削下为千仞绝壁。而江水之出其左者。至此亦始大以深。绀碧沦涟。吞吐万状。然后过郡治而西南以流其恶。而楼之所据在绝壁之上。左腋仙岭。右睇平壤。前吞银波万顷之畴。自前代以来。西路为中国往来之孔道。每盛饰楼台。以迓使客。如平壤练光亭,义州统军亭,安州百祥楼之属。皆以宏壮奇丽著于国中。而至于清爽闲远。孤特缥缈。使人临之。有凌虚御风之想。则莫不以是楼为第一。间经变故。日以颓圮。只存楹柱。观者咨嗟。余莅郡之四年。与镇帅某侯及郡中父老谋而修之。宿昔而改观焉。楼故有古今人述作。而家大人之使燕也。亦尝留诗。变故之际。板揭悉亡。乃只刻家大人诗以揭之。既乃设燕落之。镇帅以下。咸与在席。酒半。揖众言曰。今玆黄之为邑也虽小。而社稷民人之责。固自在也。以余匪才。不能获乎社稷而年岁荐饥。不能获乎民人而狱讼未尽息。则今于斯楼也。虽明月绿波。交光并照。厨传笙歌。前后杂进。而何可以尽乐哉。抑余仰明月而思。俯绿波而思。对厨传笙歌而思。曰斯楼也尚已治矣。况于社稷乎。斯楼也尚已华矣。况于民人乎。惕惕焉不敢自宁。则或者今虽不能尽乐。而他日可以尽乐乎。既以告众。遂书以自箴。
黄州郡之有月波楼。不知其创自何时。然据故老之传。盖数百年物。七点之山自北而南。至郡东北。陡然削下为千仞绝壁。而江水之出其左者。至此亦始大以深。绀碧沦涟。吞吐万状。然后过郡治而西南以流其恶。而楼之所据在绝壁之上。左腋仙岭。右睇平壤。前吞银波万顷之畴。自前代以来。西路为中国往来之孔道。每盛饰楼台。以迓使客。如平壤练光亭,义州统军亭,安州百祥楼之属。皆以宏壮奇丽著于国中。而至于清爽闲远。孤特缥缈。使人临之。有凌虚御风之想。则莫不以是楼为第一。间经变故。日以颓圮。只存楹柱。观者咨嗟。余莅郡之四年。与镇帅某侯及郡中父老谋而修之。宿昔而改观焉。楼故有古今人述作。而家大人之使燕也。亦尝留诗。变故之际。板揭悉亡。乃只刻家大人诗以揭之。既乃设燕落之。镇帅以下。咸与在席。酒半。揖众言曰。今玆黄之为邑也虽小。而社稷民人之责。固自在也。以余匪才。不能获乎社稷而年岁荐饥。不能获乎民人而狱讼未尽息。则今于斯楼也。虽明月绿波。交光并照。厨传笙歌。前后杂进。而何可以尽乐哉。抑余仰明月而思。俯绿波而思。对厨传笙歌而思。曰斯楼也尚已治矣。况于社稷乎。斯楼也尚已华矣。况于民人乎。惕惕焉不敢自宁。则或者今虽不能尽乐。而他日可以尽乐乎。既以告众。遂书以自箴。万寿圣节。弘文馆纂辑所 赐宴记。(癸卯)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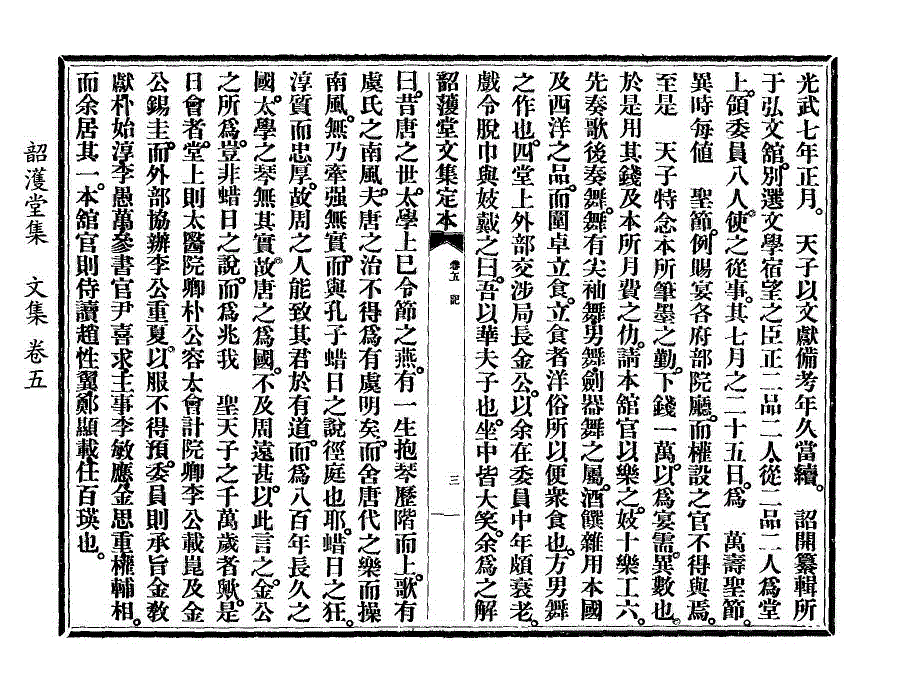 光武七年正月。 天子以文献备考年久当续。 诏开纂辑所于弘文馆。别选文学宿望之臣正二品二人,从二品二人为堂上。领委员八人。使之从事。其七月之二十五日。为 万寿圣节。异时每值 圣节。例赐宴各府部院厅。而权设之官不得与焉。至是 天子特念本所笔墨之勤。下钱一万。以为宴需。异数也。于是用其钱及本所月费之仂。请本馆官以乐之。妓十乐工六。先奏歌后奏舞。舞有尖袖舞,男舞,剑器舞之属。酒馔杂用本国及西洋之品。而围卓立食。立食者洋俗所以便众食也。方男舞之作也。四堂上外部交涉局长金公。以余在委员中年颇衰老。戏令脱巾与妓戴之曰。吾以华夫子也。坐中皆大笑。余为之解曰。昔唐之世。太学上已令节之燕。有一生抱琴历阶而上。歌有虞氏之南风。夫唐之治不得为有虞明矣。而舍唐代之乐而操南风。无乃牵强无实。而与孔子蜡日之说径庭也耶。蜡日之狂。淳质而忠厚。故周之人能致其君于有道。而为八百年长久之国。太学之琴无其实。故唐之为国。不及周远甚。以此言之。金公之所为。岂非蜡日之说。而为兆我 圣天子之千万岁者欤。是日会者。堂上则太医院卿朴公容大,会计院卿李公载昆及金公锡圭。而外部协办李公重夏。以服不得预。委员则承旨金教献,朴始淳,李愚万,参书官尹喜求,主事李敏应,金思重,权辅相。而余居其一。本馆官则侍读赵性翼,郑显载,任百瑛也。
光武七年正月。 天子以文献备考年久当续。 诏开纂辑所于弘文馆。别选文学宿望之臣正二品二人,从二品二人为堂上。领委员八人。使之从事。其七月之二十五日。为 万寿圣节。异时每值 圣节。例赐宴各府部院厅。而权设之官不得与焉。至是 天子特念本所笔墨之勤。下钱一万。以为宴需。异数也。于是用其钱及本所月费之仂。请本馆官以乐之。妓十乐工六。先奏歌后奏舞。舞有尖袖舞,男舞,剑器舞之属。酒馔杂用本国及西洋之品。而围卓立食。立食者洋俗所以便众食也。方男舞之作也。四堂上外部交涉局长金公。以余在委员中年颇衰老。戏令脱巾与妓戴之曰。吾以华夫子也。坐中皆大笑。余为之解曰。昔唐之世。太学上已令节之燕。有一生抱琴历阶而上。歌有虞氏之南风。夫唐之治不得为有虞明矣。而舍唐代之乐而操南风。无乃牵强无实。而与孔子蜡日之说径庭也耶。蜡日之狂。淳质而忠厚。故周之人能致其君于有道。而为八百年长久之国。太学之琴无其实。故唐之为国。不及周远甚。以此言之。金公之所为。岂非蜡日之说。而为兆我 圣天子之千万岁者欤。是日会者。堂上则太医院卿朴公容大,会计院卿李公载昆及金公锡圭。而外部协办李公重夏。以服不得预。委员则承旨金教献,朴始淳,李愚万,参书官尹喜求,主事李敏应,金思重,权辅相。而余居其一。本馆官则侍读赵性翼,郑显载,任百瑛也。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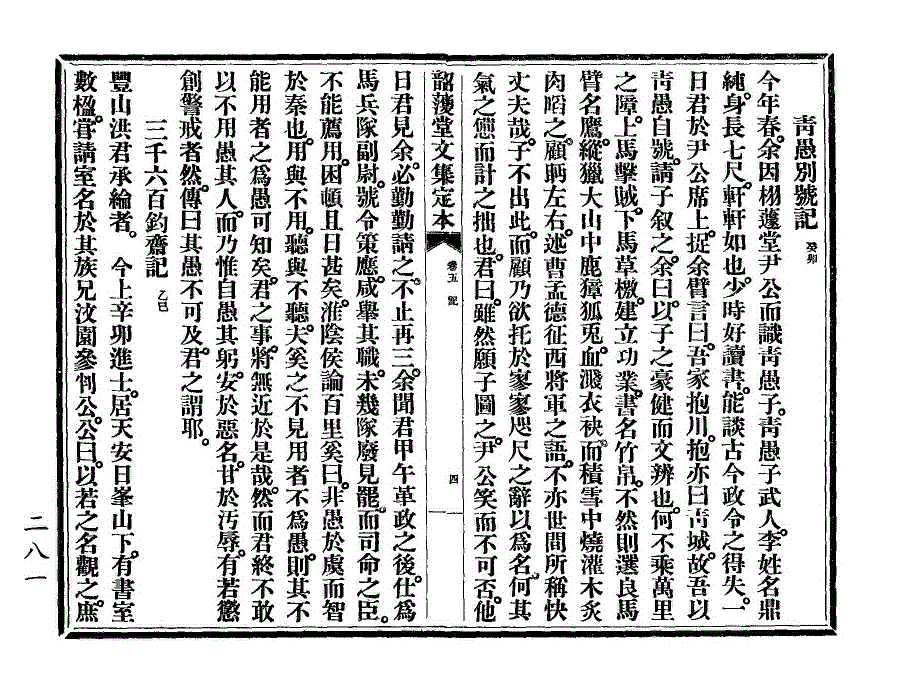 青愚别号记(癸卯)
青愚别号记(癸卯)今年春。余因栩蘧堂尹公而识青愚子。青愚子武人。李姓名鼎纯。身长七尺。轩轩如也。少时好读书。能谈古今政令之得失。一日君于尹公席上。捉余臂言曰。吾家抱川。抱亦曰青城。故吾以青愚自号。请子叙之。余曰。以子之豪健而文辨也。何不乘万里之障。上马击贼。下马草檄。建立功业。书名竹帛。不然则选良马臂名鹰。纵猎大山中鹿獐狐兔。血溅衣袂。而积雪中烧灌木炙肉啖之。顾眄左右。述曹孟德征西将军之语。不亦世间所称快丈夫哉。子不出此。而顾乃欲托于寥寥咫尺之辞以为名。何其气之惫而计之拙也。君曰。虽然愿子图之。尹公笑而不可否。他日君见余。必勤勤请之。不止再三。余闻君甲午革政之后。仕为马兵队副尉。号令策应。咸举其职。未几队废见罢。而司命之臣。不能荐用。困顿且日甚矣。淮阴侯论百里奚曰。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夫奚之不见用者不为愚。则其不能用者之为愚可知矣。君之事。将无近于是哉。然而君终不敢以不用愚其人。而乃惟自愚其躬。安于恶名。甘于污辱。有若惩创警戒者然。传曰其愚不可及。君之谓耶。
三千六百钓斋记(乙巳)
丰山洪君承纶者。 今上辛卯进士。居天安日峰山下。有书室数楹。尝请室名于其族兄汶园参判公。公曰。以若之名观之。庶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2H 页
 几其经纶者乎。乃取李太白梁父吟君不见朝歌老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流。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之语。命之曰三千六百钓斋。古之世。寄于天下者。惟有一道术而已。行此之谓经纶。宣此之谓文章。至于后世而道衰。浮散荡析。各开门户。有所谓道学家者。有所谓经纶家者。有所谓文章家者。三者迭为盛衰于历代之间。而是非纷然。何其异哉。若我 国家之俗尚。尤有异焉。首道学次文章。用舍贵贱。一准于是。而其于经纶扫如也。朝廷之上。以率由旧章为主。士大夫之间。以喜功生事为戒。惟日夜耽乐乎升平。见有或谈兵务长短及讨论疆外之事者。辄大惊以怪。指以为不祥之人。故以李文成之得位掌兵。而养兵之说。尚不得施行。卒之一朝遇难。莫能枝梧而为壬丙两年之祸厄矣。柳磻溪,丁茶山之伦。生于其后。盖尝慨其覆辙。各述经纶为书甚富。而其事已过。犹之亡羊而补牢也。言虽切而奚补哉。而况今之天下形势大变。视壬丙尤加难矣。使向之数君子当之。犹将改其虑易其算。而叹古今之殊异。汶园公之所以属意于君者。其以是欤。然窃覸君生于文学古家。飘飘有词翰才。虽其口说经济。而旧日之嗜好。尚隐然在眉宇间。如鱼鸟之于江湖山林。所安所习。猝难弃之。昔王世懋惩宋学之末弊。有言宋儒氏每讥清言致乱。不知晋宋之于江左一也。驱介冑而经生之乎。毋宁
几其经纶者乎。乃取李太白梁父吟君不见朝歌老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流。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之语。命之曰三千六百钓斋。古之世。寄于天下者。惟有一道术而已。行此之谓经纶。宣此之谓文章。至于后世而道衰。浮散荡析。各开门户。有所谓道学家者。有所谓经纶家者。有所谓文章家者。三者迭为盛衰于历代之间。而是非纷然。何其异哉。若我 国家之俗尚。尤有异焉。首道学次文章。用舍贵贱。一准于是。而其于经纶扫如也。朝廷之上。以率由旧章为主。士大夫之间。以喜功生事为戒。惟日夜耽乐乎升平。见有或谈兵务长短及讨论疆外之事者。辄大惊以怪。指以为不祥之人。故以李文成之得位掌兵。而养兵之说。尚不得施行。卒之一朝遇难。莫能枝梧而为壬丙两年之祸厄矣。柳磻溪,丁茶山之伦。生于其后。盖尝慨其覆辙。各述经纶为书甚富。而其事已过。犹之亡羊而补牢也。言虽切而奚补哉。而况今之天下形势大变。视壬丙尤加难矣。使向之数君子当之。犹将改其虑易其算。而叹古今之殊异。汶园公之所以属意于君者。其以是欤。然窃覸君生于文学古家。飘飘有词翰才。虽其口说经济。而旧日之嗜好。尚隐然在眉宇间。如鱼鸟之于江湖山林。所安所习。猝难弃之。昔王世懋惩宋学之末弊。有言宋儒氏每讥清言致乱。不知晋宋之于江左一也。驱介冑而经生之乎。毋宁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2L 页
 驱介冑而清言也。夫以末弊之虚疏无实者言之。何独道学犹晋人之清言。即经济亦或与清言而同归矣。君将若之何哉。嗟乎。吾与君俱不幸而不能生于太上道术纯一之世。以甘食美服。至老不闻金鼓之声。而徒哓哓摇烦闷之舌至于此也。可慨已。
驱介冑而清言也。夫以末弊之虚疏无实者言之。何独道学犹晋人之清言。即经济亦或与清言而同归矣。君将若之何哉。嗟乎。吾与君俱不幸而不能生于太上道术纯一之世。以甘食美服。至老不闻金鼓之声。而徒哓哓摇烦闷之舌至于此也。可慨已。巢山堂记(乙巳)
余之将之上海也。上舍生权君絅泽来示其大人巢山翁所作巢山堂记若诗。且请为堂记曰。幸子之徐戒舟人乎。余与君相识于李海鹤伯曾之寓馆者逾年。见其雍容儒雅卓出流俗。虽庸人。可以一见而知其为法家之人。则翁之为人大略。与夫为教于闺门者可知矣。翁家世出自高丽名臣正献公。正献之八世。有处士君自京师流落。居仁同之巢鹤山下。子孙世以质行文学相承袭者。至今数百年。基业日以牢固。种树日以苍茂。亲戚邻曲。佃夫臧获。日以欣悦。而鸡豚狗彘鹅鸭之胎卵。亦安其所。山不加而犹若益高。水不加而犹若益清。而自翁曾大父以下。又皆克享遐龄。以至于翁之身。年今六十有六。而五官四体强健调和。翁于是遂自以世德世业世寿三者发之于吟咏。而不嫌其近于自诧。熙熙然自足于天壤之间。如古昔上世太平之民焉。噫。今之天下。所谓万国之列强。环立相图。或标揭自由。以强民气。而古之所谓道德者变焉。或床箦波涛。往来通商。而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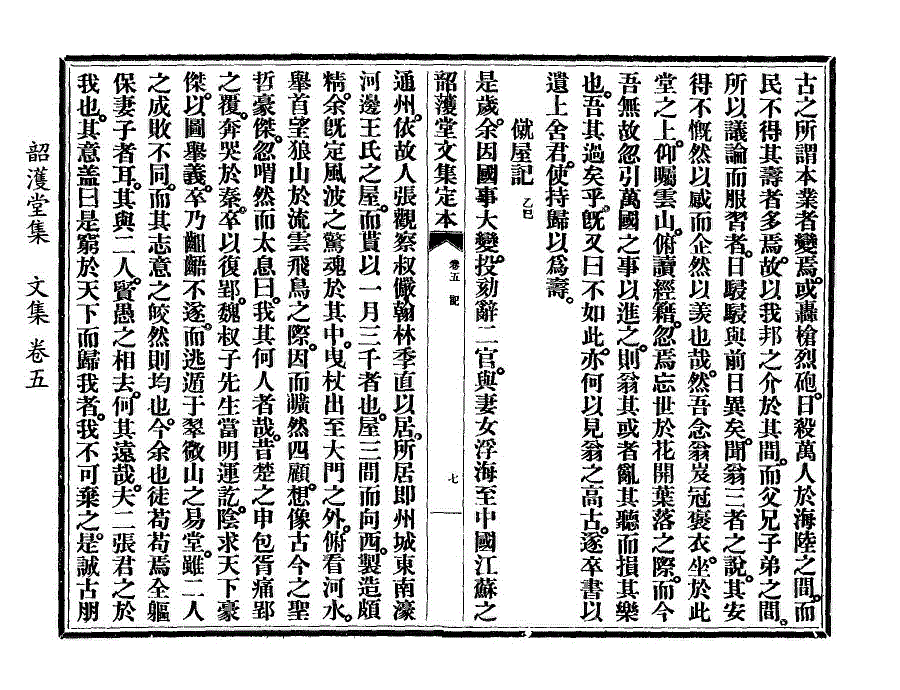 古之所谓本业者变焉。或轰枪烈炮。日杀万人于海陆之间。而民不得其寿者多焉。故以我邦之介于其间。而父兄子弟之间。所以议论而服习者。日骎骎与前日异矣。闻翁三者之说。其安得不慨然以感而企然以羡也哉。然吾念翁岌冠褒衣。坐于此堂之上。仰瞩云山。俯读经籍。忽焉忘世于花开叶落之际。而今吾无故忽引万国之事以进之。则翁其或者乱其听而损其乐也。吾其过矣乎。既又曰不如此。亦何以见翁之高古。遂卒书以遗上舍君。使持归以为寿。
古之所谓本业者变焉。或轰枪烈炮。日杀万人于海陆之间。而民不得其寿者多焉。故以我邦之介于其间。而父兄子弟之间。所以议论而服习者。日骎骎与前日异矣。闻翁三者之说。其安得不慨然以感而企然以羡也哉。然吾念翁岌冠褒衣。坐于此堂之上。仰瞩云山。俯读经籍。忽焉忘世于花开叶落之际。而今吾无故忽引万国之事以进之。则翁其或者乱其听而损其乐也。吾其过矣乎。既又曰不如此。亦何以见翁之高古。遂卒书以遗上舍君。使持归以为寿。僦屋记(乙巳)
是岁。余因国事大变。投劾辞二官。与妻女浮海至中国江苏之通州。依故人张观察叔俨,翰林季直以居。所居即州城东南濠河边王氏之屋。而贳以一月三千者也。屋三间而向西。制造颇精。余既定风波之惊魂于其中。曳杖出至大门之外。俯看河水。举首望狼山于流云飞鸟之际。因而旷然四顾。想像古今之圣哲豪杰。忽喟然而太息曰。我其何人者哉。昔楚之申包胥痛郢之覆。奔哭于秦。卒以复郢。魏叔子先生当明运讫。阴求天下豪杰。以图举义。卒乃龃龉不遂。而逃遁于翠微山之易堂。虽二人之成败不同。而其志意之皎然则均也。今余也徒苟苟焉全躯保妻子者耳。其与二人。贤愚之相去。何其远哉。夫二张君之于我也。其意盖曰是穷于天下而归我者。我不可弃之。是诚古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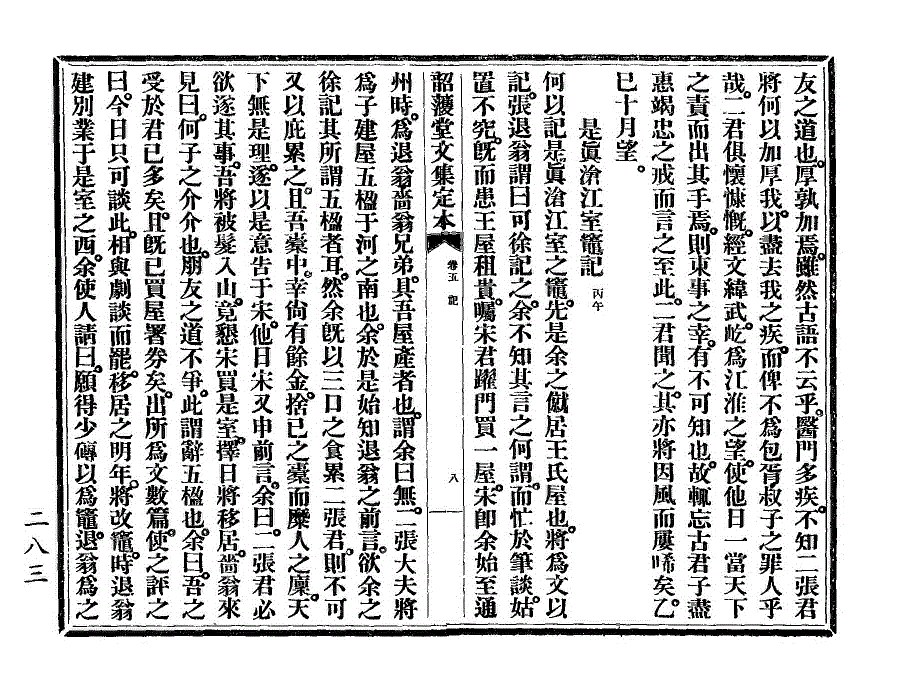 友之道也。厚孰加焉。虽然古语不云乎。医门多疾。不知二张君将何以加厚我。以尽去我之疾。而俾不为包胥,叔子之罪人乎哉。二君俱怀慷慨。经文纬武。屹为江淮之望。使他日一当天下之责而出其手焉。则东事之幸。有不可知也。故辄忘古君子尽惠竭忠之戒而言之至此。二君闻之。其亦将因风而屡唏矣。乙巳十月望。
友之道也。厚孰加焉。虽然古语不云乎。医门多疾。不知二张君将何以加厚我。以尽去我之疾。而俾不为包胥,叔子之罪人乎哉。二君俱怀慷慨。经文纬武。屹为江淮之望。使他日一当天下之责而出其手焉。则东事之幸。有不可知也。故辄忘古君子尽惠竭忠之戒而言之至此。二君闻之。其亦将因风而屡唏矣。乙巳十月望。是真沧江室灶记(丙午)
何以记是真沧江室之灶。先是余之僦居王氏屋也。将为文以记。张退翁谓曰可徐记之。余不知其言之何谓。而忙于笔谈。姑置不究。既而患王屋租贵。嘱宋君跃门买一屋。宋即余始至通州时。为退翁,啬翁兄弟。具吾屋产者也。谓余曰无。二张大夫将为子建屋五楹于河之南也。余于是始知退翁之前言。欲余之徐记其所谓五楹者耳。然余既以三口之食累二张君。则不可又以庇累之。且吾橐中。幸尚有馀金。舍己之橐而糜人之廪。天下无是理。遂以是意告于宋。他日宋又申前言。余曰。二张君必欲遂其事。吾将被发入山。竟恳宋买是室。择日将移居。啬翁来见曰。何子之介介也。朋友之道不争。此谓辞五楹也。余曰。吾之受于君已多矣。且既已买屋署券矣。出所为文数篇。使之评之曰。今日只可谈此。相与剧谈而罢。移居之明年。将改灶。时退翁建别业于是室之西。余使人请曰。愿得少砖以为灶。退翁为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4H 页
 欣然送砖二百。余遂以改灶。所以成五楹之意也。昔陶靖节先生每作饭。见火发而拜。拜于灶也。大哉灶之时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诗曰粒我烝民。莫非尔极。其灶之谓乎。爰记之。以存二张子天下长者者之志。
欣然送砖二百。余遂以改灶。所以成五楹之意也。昔陶靖节先生每作饭。见火发而拜。拜于灶也。大哉灶之时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诗曰粒我烝民。莫非尔极。其灶之谓乎。爰记之。以存二张子天下长者者之志。丙午五月十三日。游南通翰墨林书局莲池记。(丙午)
是日稍热。余坐书局北窗下。校印书数纸罢。视日向晡矣。揭君向寅。忽呼余指窗外莲池。趋而出。余意其有游。寻踵之。揭不见。独见王君汝宏。立于池西北隅。俯视舟。见余招之。余就问揭所在。王南望而手之。余至通州日浅。未解中国语。故人之接余者。其用多在于目若手而少在于口也。方欲再问。见揭携一竹竿来。将以为篙也。于是王先入舟。余次之。揭又次之。而舟缆系在桃树。余手解其缆。揭乃篙而放于池心。时莲叶被池面者。仅十之七八。花始半开。香气隐然。而舟腹摩莲叶而过。淅然有声。余恐叶之被伤。颇怀懊恨。既而回视其过处。则叶故无恙。余又窃为之喜焉。行至池半折而北而东。缘堤蒲柳芦苇之属。参差濛密。拂摩舟舷。与莲叶之声相和。益可听。尽池之东。有老柳二株垂荫甚邃。乃抵舟其间。以避晷烘。良久转而南而西。见乱叶之中有大小二藕。而舟适驶掠小藕而过。余急伸臂把藕折之。王在背后大声呼芙蓉。犹若惊愕爱惜。然所以成余之美也。遂乃折行西北而复焉系舟以归。王江苏无锡人。淹贯群籍。通达时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4L 页
 务。主局务者有年矣。揭江西东乡人。偶客于局。与余同室。志趣淳笃。方精攻地理。使余忘万里羁旅之忧者非二人耶。盖前之记重游。而后之记重人也。如其不然而徒以游而已也。则彼大江南北千百陂塘风露流香之际。扣船舷而唱欸乃者。其何限哉。
务。主局务者有年矣。揭江西东乡人。偶客于局。与余同室。志趣淳笃。方精攻地理。使余忘万里羁旅之忧者非二人耶。盖前之记重游。而后之记重人也。如其不然而徒以游而已也。则彼大江南北千百陂塘风露流香之际。扣船舷而唱欸乃者。其何限哉。是真沧江室记(丁未)
卧见船旗之猎猎拂东门外桑树枝而过者。是真沧江之室也。室之主人。自少自号沧江。而所居实无江水。私尝已记其实矣。岁乙巳。自韩至中国江苏之通州。依张退庵,啬庵兄弟二大夫。僦一屋以居。未几买屋于僦居左偏移处焉。即州城之东南濒河处也。通之为州。西北有小河水过唐家闸经州城。东南流百馀里入海。而南离唐家闸六七里。河水分。一支东趋经州城北。以合于干流。其形如环。遂为城濠。则主人之居。实类岛居。而其于水也。始能餍饫极矣。此室之所以得名。而啬庵所为作额字以扬之者也。门之外。常有渔舟一二来宿。语声拉杂。犹之邻户。商舶之往来者。朝夕如织。而时有小火轮船。曳一二舶以行。若鱼贯然。其外又有踏桨而驱鱼者。使鸬鹚而取鱼者。时时群集以嚣。而河岸之外。竹树被野。人家隐现。平远冥濛。若无际涯。忽然见狼山剑山数峰峦。騀然耸出于南方一二十里之外。如大海帆樯之被风打阻而停。以立于浪涛之间。此又河水所以资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5H 页
 乎外。以益美之实境也。屋故颇壮而中圮三之一。主人或葺或刱。既又以暑甚。窗中堂之北壁。其圮者治而田之。以种菜谷。庭有枇杷橘竹各一。而橘与竹则主人之所新种也。或曰。子去国万里。始得其居。以实其名。以赅其观。此亦天下之至奇也。子可以此为乐。不可曰吾何以至此而惘惘为也。主人微笑。姑不答。(名室之三年始作记。)
乎外。以益美之实境也。屋故颇壮而中圮三之一。主人或葺或刱。既又以暑甚。窗中堂之北壁。其圮者治而田之。以种菜谷。庭有枇杷橘竹各一。而橘与竹则主人之所新种也。或曰。子去国万里。始得其居。以实其名。以赅其观。此亦天下之至奇也。子可以此为乐。不可曰吾何以至此而惘惘为也。主人微笑。姑不答。(名室之三年始作记。)省庵记(癸丑)
呼余为乡先生而问及文字者。有曰文先其人。近请记其所号省庵曰。门生年今四十矣。行且与草木虫豸同腐。愿藉先生文以传。余曰噫嘻。夫人之所赖以传者。非君国耶。生也其名传于朝报。没也其功传于竹帛。皆因君国而有也。呜呼。今我韩之君国安在哉。夫其失于君国如此。则惟道德与文章。可以自传。然君于斯又未可谓之至焉。则其言之悲。固宜至此。余之文虽不足以传君。而所以图其传者。乌能已已哉。书曰是姓李。名箕绍者也。曰传矣。曰未也。是本安岳人。后为开城人者也。曰传之详矣。曰未也。是于隆熙中。仕为宫内府主事。隶掌礼院。车轮曳踵于俎豆钟鼓之间岁馀。无其阙而罢者也。曰已详矣。曰未也。其面长而晰。其性温温然。若其所谓省庵者。本于曾子之一日三省。然曾子急于内而不暇虑传者。故姑不详言。以警其进。斯义也古之人谓之爱人以德。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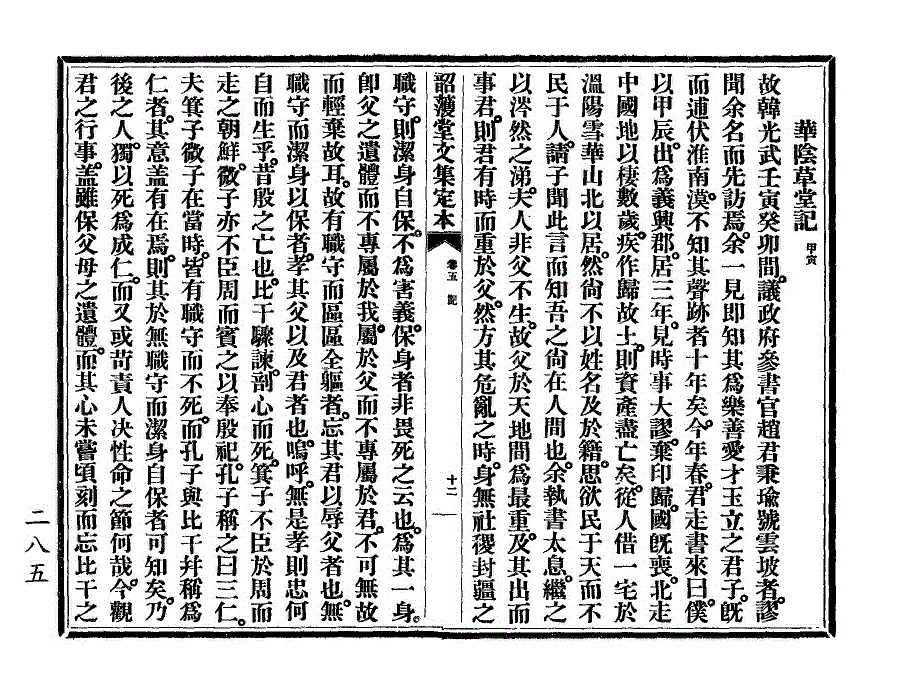 华阴草堂记(甲寅)
华阴草堂记(甲寅)故韩光武壬寅癸卯间。议政府参书官赵君秉瑜号云坡者。谬闻余名而先访焉。余一见即知其为乐善爱才玉立之君子。既而逋伏淮南。漠不知其声迹者十年矣。今年春。君走书来曰。仆以甲辰。出为义兴郡。居三年。见时事大谬。弃印归。国既丧。北走中国地以栖数岁。疾作归故土。则资产尽亡矣。从人借一宅于温阳雪华山北以居。然尚不以姓名及于籍。思欲民于天而不民于人。请子闻此言而知吾之尚在人间也。余执书太息。继之以涔然之涕。夫人非父不生。故父于天地间为最重。及其出而事君。则君有时而重于父。然方其危乱之时。身无社稷封疆之职守。则洁身自保。不为害义。保身者非畏死之云也。为其一身。即父之遗体而不专属于我。属于父而不专属于君。不可无故而轻弃故耳。故有职守而区区全躯者。忘其君以辱父者也。无职守而洁身以保者。孝其父以及君者也。呜呼。无是孝则忠何自而生乎。昔殷之亡也。比干骤谏。剖心而死。箕子不臣于周而走之朝鲜。微子亦不臣周而宾之以奉殷祀。孔子称之曰三仁。夫箕子微子在当时。皆有职守而不死。而孔子与比干并称为仁者。其意盖有在焉。则其于无职守而洁身自保者可知矣。乃后之人。独以死为成仁。而又或苛责人决性命之节何哉。今观君之行事。盖虽保父母之遗体。而其心未尝顷刻而忘比干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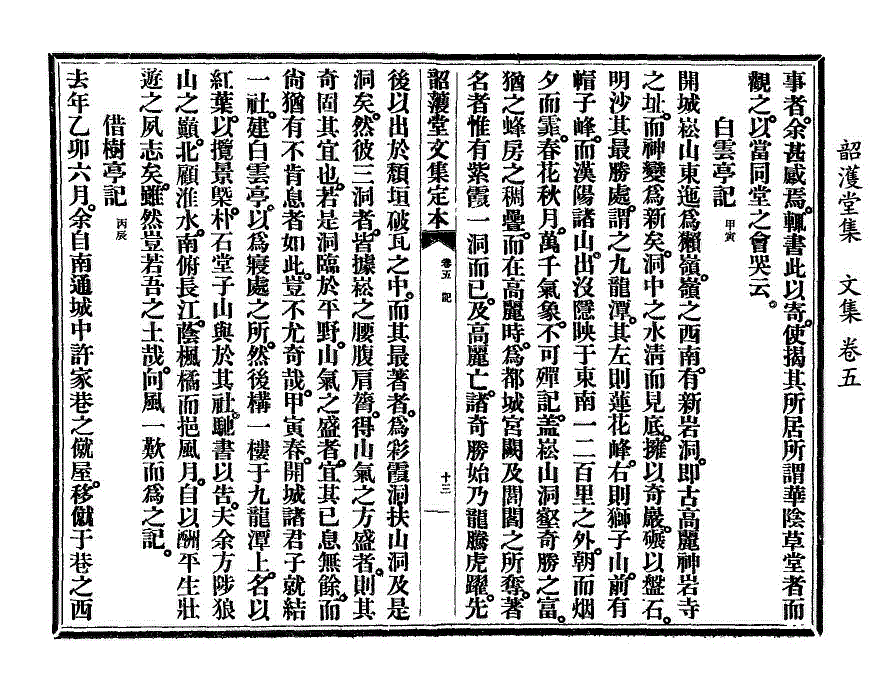 事者。余甚感焉。辄书此以寄。使揭其所居所谓华阴草堂者而观之。以当同堂之会哭云。
事者。余甚感焉。辄书此以寄。使揭其所居所谓华阴草堂者而观之。以当同堂之会哭云。白云亭记(甲寅)
开城崧山东迤为獭岭。岭之西南。有新岩洞。即古高丽神岩寺之址。而神变为新矣。洞中之水清而见底。拥以奇岩。碾以盘石。明沙其最胜处。谓之九龙潭。其左则莲花峰。右则狮子山。前有帽子峰。而汉阳诸山。出没隐映于东南一二百里之外。朝而烟夕而霏。春花秋月。万千气象。不可殚记。盖崧山洞壑奇胜之富。犹之蜂房之稠叠。而在高丽时。为都城宫阙及闾阎之所夺。著名者惟有紫霞一洞而已。及高丽亡。诸奇胜始乃龙腾虎跃。先后以出于颓垣破瓦之中。而其最著者。为彩霞洞,扶山洞及是洞矣。然彼三洞者。皆据崧之腰腹肩膂。得山气之方盛者。则其奇固其宜也。若是洞临于平野。山气之盛者。宜其已息无馀。而尚犹有不肯息者如此。岂不尤奇哉。甲寅春。开城诸君子就结一社。建白云亭。以为寝处之所。然后构一楼于九龙潭上。名以红叶。以揽景槩。朴石堂子山与于其社。驰书以告。夫余方陟狼山之巅。北顾淮水。南俯长江。荫枫橘而挹风月。自以酬平生壮游之夙志矣。虽然岂若吾之土哉。向风一叹而为之记。
借树亭记(丙辰)
去年乙卯六月。余自南通城中许家巷之僦屋。移僦于巷之西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6L 页
 南十馀武地之屋。屋稍耸净。而庭窄无种植。惟西墙之外有一宅。本明遗民进士包壮行先生之所筑。名以石圃者。而宅中女贞树一株竦立千尺。终日送翠。滴滴如也。人之始至者。莫不认为是屋之有。既而知其非而将为之怅然。此屋之所以命为借树亭者也。夫借者。非已有而不久将还之词也。故彼穹然之天。隤然之地。古之旷达者。亦或视为逆旅借居之不久将还者。而况是树者。安可以借为奇而著之名乎。虽然今不借是树。则无以挹包先生之高风远韵而亲之于朝夕之间。此实区区之志之所寓也。呜呼。是志也苟余能洞洞属属。持而勿丧。不以利昏。不以穷滥。不以威挠。则其将还之于谁。志既不可还。则其为志之所寓者。独将何如哉。试以问之树。
南十馀武地之屋。屋稍耸净。而庭窄无种植。惟西墙之外有一宅。本明遗民进士包壮行先生之所筑。名以石圃者。而宅中女贞树一株竦立千尺。终日送翠。滴滴如也。人之始至者。莫不认为是屋之有。既而知其非而将为之怅然。此屋之所以命为借树亭者也。夫借者。非已有而不久将还之词也。故彼穹然之天。隤然之地。古之旷达者。亦或视为逆旅借居之不久将还者。而况是树者。安可以借为奇而著之名乎。虽然今不借是树。则无以挹包先生之高风远韵而亲之于朝夕之间。此实区区之志之所寓也。呜呼。是志也苟余能洞洞属属。持而勿丧。不以利昏。不以穷滥。不以威挠。则其将还之于谁。志既不可还。则其为志之所寓者。独将何如哉。试以问之树。泗阳书室记(丙辰)
山清健斋子所居泗阳书室。即其先人正言公之遗庐也。泗阳者。其地有一大溪。名曰泗水。故正言公以之推想乎孔子所居洙泗之间而志之云。呜呼。于斯之世。杂教之与孔子为敌者。李耳,如来之外。又不可胜数。故见今中国以民而主天下之议论者。大抵多杂教之人。或以为孔子之道专制而非共和。或以为待孔子宜与他教等而不可独尊。或以为孔子之道哲学而非宗教。或以为阙里之祠可毁。吾道之存者。只如一发。而阙里数亩之宫。殆哉其岌岌。崔健斋之泗阳书室。何为者哉。然在易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7H 页
 剥。一阳独存于上。谓之硕果不食。故有康南海氏者出。慨然以为孔教者中国之国教。国教亡。国安得独存。遂飞书政府。极论其事。以掴主议者之颊。诸省熊蹲虎踞之悍将帅闻而感之。亦相与拔大剑以向之。于是杂教民之主议者。始乃稍稍内慑。姑敛其吻。夫古之君子之道。时其静也。卷之若蠖。时其动也。奋之若龙。乃后世之士则不然。或以太过于枯寂。视天下之事功。犹之粪尿然。则使康南海氏处于今日。饮水读书于空山之中。而不动一手一足。至其孔教已亡孔祠已毁而后。始乃洋洋作千万言。徒以空言泄其感痛。其何益之有哉。故夫能不偏于枯寂然后。可以有为。可以有为然后。可以扶孔教。孔教扶则阙里祠存。而泗阳书室。亦可以存矣。吾恐健斋子块坐读书。嘐嘐孔子。而深山穷谷之中。难以得闻天下之大事。故因风一诵此。
剥。一阳独存于上。谓之硕果不食。故有康南海氏者出。慨然以为孔教者中国之国教。国教亡。国安得独存。遂飞书政府。极论其事。以掴主议者之颊。诸省熊蹲虎踞之悍将帅闻而感之。亦相与拔大剑以向之。于是杂教民之主议者。始乃稍稍内慑。姑敛其吻。夫古之君子之道。时其静也。卷之若蠖。时其动也。奋之若龙。乃后世之士则不然。或以太过于枯寂。视天下之事功。犹之粪尿然。则使康南海氏处于今日。饮水读书于空山之中。而不动一手一足。至其孔教已亡孔祠已毁而后。始乃洋洋作千万言。徒以空言泄其感痛。其何益之有哉。故夫能不偏于枯寂然后。可以有为。可以有为然后。可以扶孔教。孔教扶则阙里祠存。而泗阳书室。亦可以存矣。吾恐健斋子块坐读书。嘐嘐孔子。而深山穷谷之中。难以得闻天下之大事。故因风一诵此。永类斋记(丁巳)
咸安之赵。以韩 端宗忠臣贞节公渔溪先生讳旅为祖者。族华而蕃。其一支居谷城。传至讳某。事亲至孝。褒赠童蒙教官。子孙皆绳趋矩步。为一邑法家。五世有曰性祺君者。文学士也。尝慨然以为自周以后二千年。天下之孝道不如古者。由聚族合食之礼之寝也。与族侄监役仁奎谋。鬻宗庄之地。建一屋于里中胜区。以为聚族之所。事才有绪。而仁奎遽殒。君尤痛恨不宁。令族侄炳奎踵仁奎以辅。戮力建屋凡若干楹。不侈不陋。以今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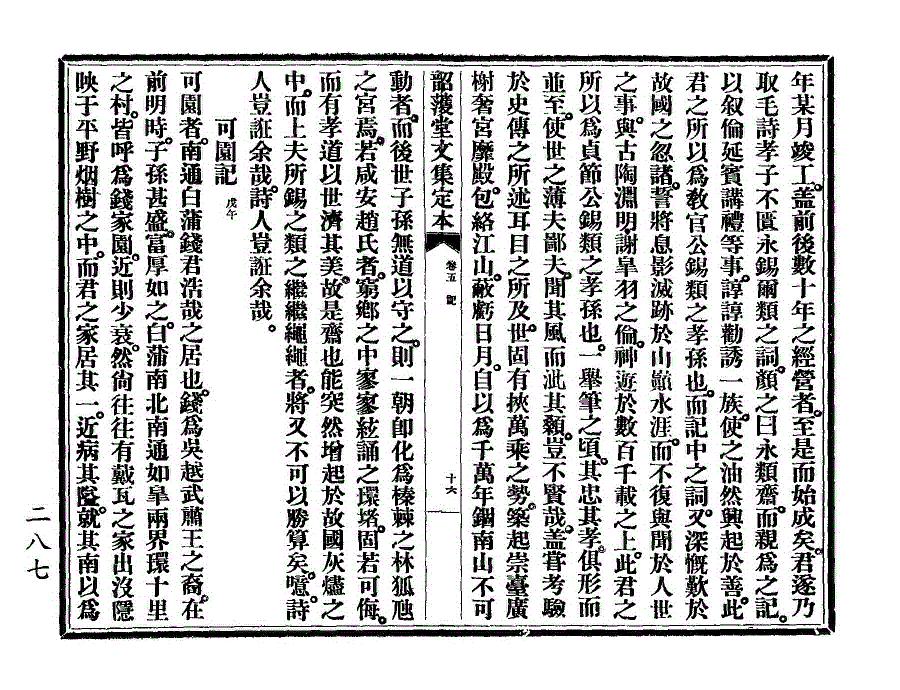 年某月竣工。盖前后数十年之经营者。至是而始成矣。君遂乃取毛诗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词。颜之曰永类斋。而亲为之记。以叙伦延宾讲礼等事。谆谆劝诱一族。使之油然兴起于善。此君之所以为教官公锡类之孝孙也。而记中之词。又深慨叹于故国之忽诸。誓将息影灭迹于山巅水涯。而不复与闻于人世之事。与古陶渊明,谢皋羽之伦。神游于数百千载之上。此君之所以为贞节公锡类之孝孙也。一举笔之顷。其忠其孝。俱形而并至。使世之薄夫鄙夫。闻其风而泚其颡。岂不贤哉。盖尝考验于史传之所述耳目之所及。世固有挟万乘之势。筑起崇台广榭奢宫靡殿。包络江山。蔽亏日月。自以为千万年锢南山不可动者。而后世子孙无道以守之。则一朝即化为榛棘之林狐虺之宫焉。若咸安赵氏者。穷乡之中寥寥弦诵之环堵。固若可侮。而有孝道以世济其美。故是斋也能突然增起于故国灰烬之中。而上夫所锡之类之继继绳绳者。将又不可以胜算矣。噫。诗人岂诳余哉。诗人岂诳余哉。
年某月竣工。盖前后数十年之经营者。至是而始成矣。君遂乃取毛诗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词。颜之曰永类斋。而亲为之记。以叙伦延宾讲礼等事。谆谆劝诱一族。使之油然兴起于善。此君之所以为教官公锡类之孝孙也。而记中之词。又深慨叹于故国之忽诸。誓将息影灭迹于山巅水涯。而不复与闻于人世之事。与古陶渊明,谢皋羽之伦。神游于数百千载之上。此君之所以为贞节公锡类之孝孙也。一举笔之顷。其忠其孝。俱形而并至。使世之薄夫鄙夫。闻其风而泚其颡。岂不贤哉。盖尝考验于史传之所述耳目之所及。世固有挟万乘之势。筑起崇台广榭奢宫靡殿。包络江山。蔽亏日月。自以为千万年锢南山不可动者。而后世子孙无道以守之。则一朝即化为榛棘之林狐虺之宫焉。若咸安赵氏者。穷乡之中寥寥弦诵之环堵。固若可侮。而有孝道以世济其美。故是斋也能突然增起于故国灰烬之中。而上夫所锡之类之继继绳绳者。将又不可以胜算矣。噫。诗人岂诳余哉。诗人岂诳余哉。可园记(戊午)
可园者。南通白蒲钱君浩哉之居也。钱为吴越武肃王之裔。在前明时。子孙甚盛。富厚如之。白蒲南北南通如皋两界环十里之村。皆呼为钱家园。近则少衰。然尚往往有戴瓦之家出没隐映于平野烟树之中。而君之家居其一。近病其隘。就其南以为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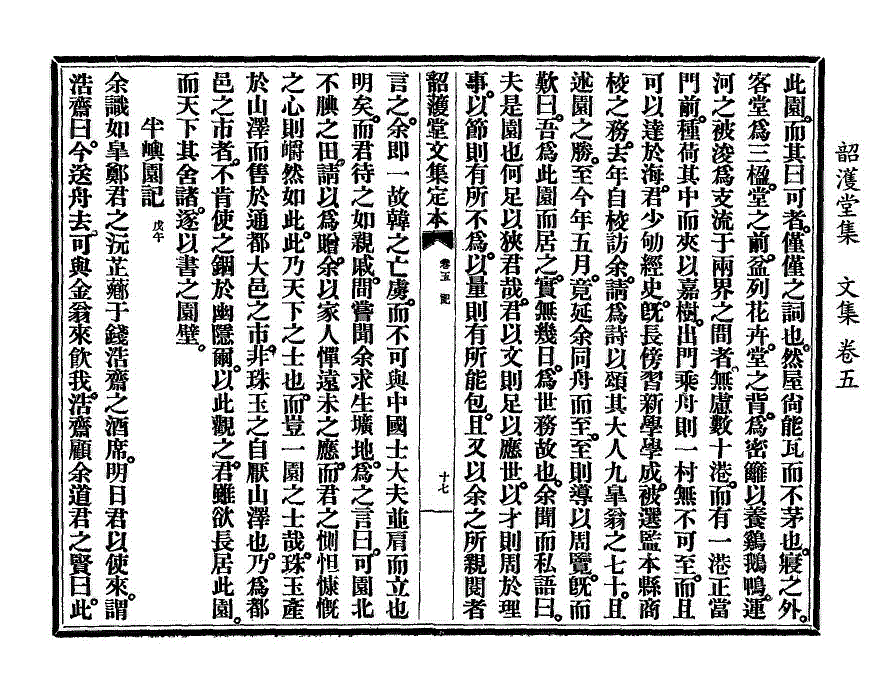 此园。而其曰可者。仅仅之词也。然屋尚能瓦而不茅也。寝之外。客堂为三楹。堂之前。盆列花卉。堂之背。为密篱以养鸡鹅鸭。运河之被浚为支流于两界之间者。无虑数十港。而有一港正当门前。种荷其中而夹以嘉树。出门乘舟则一村无不可至。而且可以达于海。君少劬经史。既长傍习新学学成。被选监本县商校之务。去年自校访余。请为诗以颂其大人九皋翁之七十。且述园之胜。至今年五月。竟延余同舟而至。至则导以周览。既而叹曰。吾为此园而居之。实无几日。为世务故也。余闻而私语曰。夫是园也何足以狭君哉。君以文则足以应世。以才则周于理事。以节则有所不为。以量则有所能包。且又以余之所亲阅者言之。余即一故韩之亡虏。而不可与中国士大夫并肩而立也明矣。而君待之如亲戚。间尝闻余求生圹地。为之言曰。可园北不腆之田。请以为赠。余以家人惮远未之应。而君之恻怛慷慨之心则皭然如此。此乃天下之士也。而岂一园之士哉。珠玉产于山泽而售于通都大邑之市。非珠玉之自厌山泽也。乃为都邑之市者。不肯使之锢于幽隐尔。以此观之。君虽欲长居此园。而天下其舍诸。遂以书之园壁。
此园。而其曰可者。仅仅之词也。然屋尚能瓦而不茅也。寝之外。客堂为三楹。堂之前。盆列花卉。堂之背。为密篱以养鸡鹅鸭。运河之被浚为支流于两界之间者。无虑数十港。而有一港正当门前。种荷其中而夹以嘉树。出门乘舟则一村无不可至。而且可以达于海。君少劬经史。既长傍习新学学成。被选监本县商校之务。去年自校访余。请为诗以颂其大人九皋翁之七十。且述园之胜。至今年五月。竟延余同舟而至。至则导以周览。既而叹曰。吾为此园而居之。实无几日。为世务故也。余闻而私语曰。夫是园也何足以狭君哉。君以文则足以应世。以才则周于理事。以节则有所不为。以量则有所能包。且又以余之所亲阅者言之。余即一故韩之亡虏。而不可与中国士大夫并肩而立也明矣。而君待之如亲戚。间尝闻余求生圹地。为之言曰。可园北不腆之田。请以为赠。余以家人惮远未之应。而君之恻怛慷慨之心则皭然如此。此乃天下之士也。而岂一园之士哉。珠玉产于山泽而售于通都大邑之市。非珠玉之自厌山泽也。乃为都邑之市者。不肯使之锢于幽隐尔。以此观之。君虽欲长居此园。而天下其舍诸。遂以书之园壁。半屿园记(戊午)
余识如皋郑君之沅芷芗于钱浩斋之酒席。明日君以使来。谓浩斋曰。今送舟去。可与金翁来饮我。浩斋顾余道君之贤曰。此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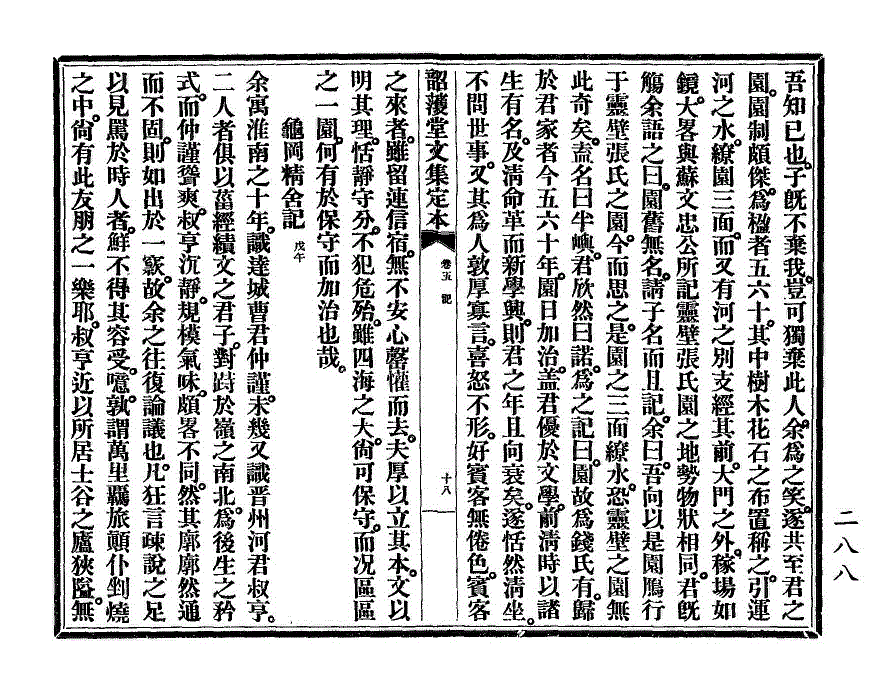 吾知己也。子既不弃我。岂可独弃此人。余为之笑。遂共至君之园。园制颇杰。为楹者五六十。其中树木花石之布置称之。引运河之水。缭园三面。而又有河之别支经其前。大门之外。稼场如镜。大略与苏文忠公所记灵壁张氏园之地势物状相同。君既觞余语之曰。园旧无名。请子名而且记。余曰。吾向以是园雁行于灵壁张氏之园。今而思之。是园之三面缭水。恐灵壁之园无此奇矣。盍名曰半屿。君欣然曰诺。为之记曰。园故为钱氏有。归于君家者今五六十年。园日加治。盖君优于文学。前清时以诸生有名。及清命革而新学兴。则君之年且向衰矣。遂恬然清坐。不问世事。又其为人敦厚寡言。喜怒不形。好宾客无倦色。宾客之来者。虽留连信宿。无不安心罄欢而去。夫厚以立其本。文以明其理。恬静守分。不犯危殆。虽四海之大。尚可保守。而况区区之一园。何有于保守而加治也哉。
吾知己也。子既不弃我。岂可独弃此人。余为之笑。遂共至君之园。园制颇杰。为楹者五六十。其中树木花石之布置称之。引运河之水。缭园三面。而又有河之别支经其前。大门之外。稼场如镜。大略与苏文忠公所记灵壁张氏园之地势物状相同。君既觞余语之曰。园旧无名。请子名而且记。余曰。吾向以是园雁行于灵壁张氏之园。今而思之。是园之三面缭水。恐灵壁之园无此奇矣。盍名曰半屿。君欣然曰诺。为之记曰。园故为钱氏有。归于君家者今五六十年。园日加治。盖君优于文学。前清时以诸生有名。及清命革而新学兴。则君之年且向衰矣。遂恬然清坐。不问世事。又其为人敦厚寡言。喜怒不形。好宾客无倦色。宾客之来者。虽留连信宿。无不安心罄欢而去。夫厚以立其本。文以明其理。恬静守分。不犯危殆。虽四海之大。尚可保守。而况区区之一园。何有于保守而加治也哉。龟冈精舍记(戊午)
余寓淮南之十年。识达城曹君仲谨。未几又识晋州河君叔亨。二人者俱以菑经绩文之君子。对跱于岭之南北。为后生之矜式。而仲谨耸爽。叔亨沉静。规模气味。颇略不同。然其廓廓然通而不固。则如出于一窾。故余之往复论议也。凡狂言疏说之足以见骂于时人者。鲜不得其容受。噫。孰谓万里羁旅颠仆剉烧之中。尚有此友朋之一乐耶。叔亨近以所居士谷之庐狭隘。无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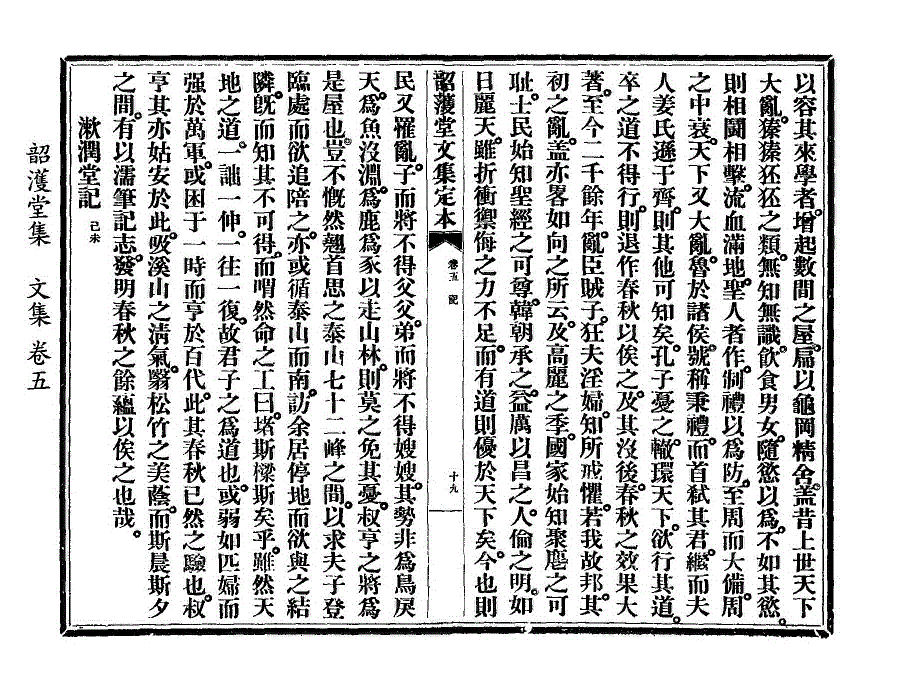 以容其来学者。增起数间之屋。扁以龟冈精舍。盖昔上世天下大乱。獉獉狉狉之类。无知无识。饮食男女。随欲以为。不如其欲。则相斗相击。流血满地。圣人者作。制礼以为防。至周而大备。周之中衰。天下又大乱。鲁于诸侯。号称秉礼。而首弑其君。继而夫人姜氏逊于齐。则其他可知矣。孔子忧之。辙环天下。欲行其道。卒之道不得行。则退作春秋以俟之。及其没后。春秋之效果大著。至今二千馀年。乱臣贼子。狂夫淫妇。知所戒惧。若我故邦。其初之乱。盖亦略如向之所云。及高丽之季。国家始知聚麀之可耻。士民始知圣经之可尊。韩朝承之。益厉以昌之。人伦之明。如日丽天。虽折冲御侮之力不足。而有道则优于天下矣。今也则民又罹乱。子而将不得父父。弟而将不得嫂嫂。其势非为鸟戾天。为鱼没渊。为鹿为豕以走山林。则莫之免其忧。叔亨之将为是屋也。岂不慨然翘首思之泰山七十二峰之间。以求夫子登临处而欲追陪之。亦或循泰山而南。访余居停地而欲与之结邻。既而知其不可得。而喟然命之工曰。堵斯梁斯矣乎。虽然天地之道。一诎一伸。一往一复。故君子之为道也。或弱如匹妇而强于万军。或困于一时而亨于百代。此其春秋已然之验也。叔亨其亦姑安于此。吸溪山之清气。翳松竹之美荫。而斯晨斯夕之间。有以濡笔记志。发明春秋之馀蕴以俟之也哉。
以容其来学者。增起数间之屋。扁以龟冈精舍。盖昔上世天下大乱。獉獉狉狉之类。无知无识。饮食男女。随欲以为。不如其欲。则相斗相击。流血满地。圣人者作。制礼以为防。至周而大备。周之中衰。天下又大乱。鲁于诸侯。号称秉礼。而首弑其君。继而夫人姜氏逊于齐。则其他可知矣。孔子忧之。辙环天下。欲行其道。卒之道不得行。则退作春秋以俟之。及其没后。春秋之效果大著。至今二千馀年。乱臣贼子。狂夫淫妇。知所戒惧。若我故邦。其初之乱。盖亦略如向之所云。及高丽之季。国家始知聚麀之可耻。士民始知圣经之可尊。韩朝承之。益厉以昌之。人伦之明。如日丽天。虽折冲御侮之力不足。而有道则优于天下矣。今也则民又罹乱。子而将不得父父。弟而将不得嫂嫂。其势非为鸟戾天。为鱼没渊。为鹿为豕以走山林。则莫之免其忧。叔亨之将为是屋也。岂不慨然翘首思之泰山七十二峰之间。以求夫子登临处而欲追陪之。亦或循泰山而南。访余居停地而欲与之结邻。既而知其不可得。而喟然命之工曰。堵斯梁斯矣乎。虽然天地之道。一诎一伸。一往一复。故君子之为道也。或弱如匹妇而强于万军。或困于一时而亨于百代。此其春秋已然之验也。叔亨其亦姑安于此。吸溪山之清气。翳松竹之美荫。而斯晨斯夕之间。有以濡笔记志。发明春秋之馀蕴以俟之也哉。漱润堂记(己未)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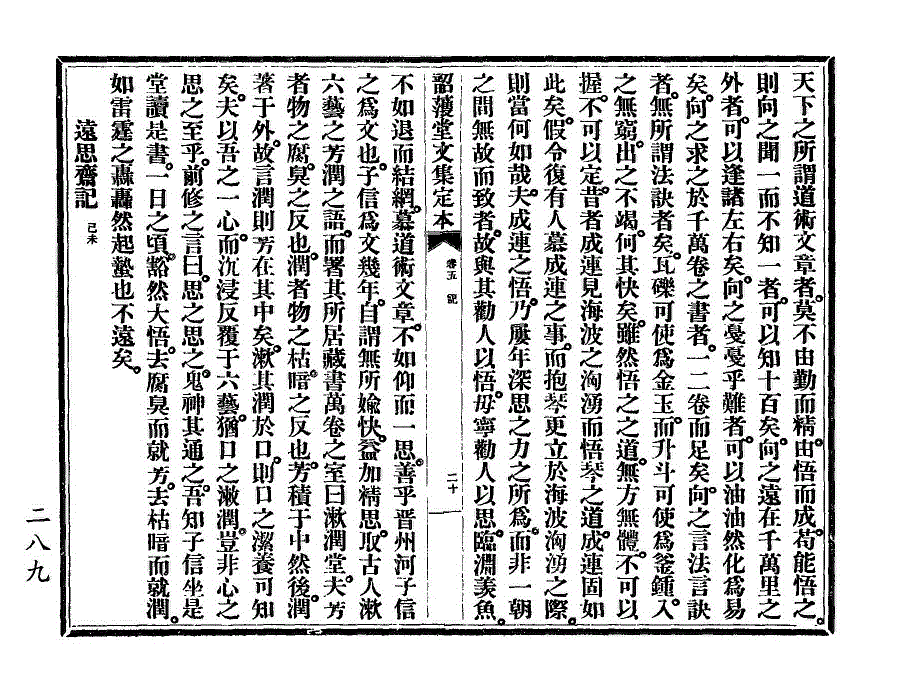 天下之所谓道术文章者。莫不由勤而精。由悟而成。苟能悟之。则向之闻一而不知一者。可以知十百矣。向之远在千万里之外者。可以逢诸左右矣。向之戛戛乎难者。可以油油然化为易矣。向之求之于千万卷之书者。一二卷而足矣。向之言法言诀者。无所谓法诀者矣。瓦砾可使为金玉。而升斗可使为釜钟。入之无穷。出之不竭。何其快矣。虽然悟之之道。无方无体。不可以握。不可以定。昔者成连见海波之汹涌而悟琴之道。成连固如此矣。假令复有人慕成连之事。而抱琴更立于海波汹涌之际。则当何如哉。夫成连之悟。乃屡年深思之力之所为。而非一朝之间无故而致者。故与其劝人以悟。毋宁劝人以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慕道术文章。不如仰而一思。善乎晋州河子信之为文也。子信为文几年。自谓无所媮快。益加精思。取古人漱六艺之芳润之语。而署其所居藏书万卷之室曰漱润堂。夫芳者物之腐。臭之反也。润者物之枯。暗之反也。芳积于中然后。润著于外。故言润则芳在其中矣。漱其润于口。则口之洁养可知矣。夫以吾之一心。而沉浸反覆于六艺。犹口之漱润。岂非心之思之至乎。前修之言曰。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吾知子信坐是堂读是书。一日之顷。豁然大悟。去腐臭而就芳。去枯暗而就润。如雷霆之轰轰然起蛰也不远矣。
天下之所谓道术文章者。莫不由勤而精。由悟而成。苟能悟之。则向之闻一而不知一者。可以知十百矣。向之远在千万里之外者。可以逢诸左右矣。向之戛戛乎难者。可以油油然化为易矣。向之求之于千万卷之书者。一二卷而足矣。向之言法言诀者。无所谓法诀者矣。瓦砾可使为金玉。而升斗可使为釜钟。入之无穷。出之不竭。何其快矣。虽然悟之之道。无方无体。不可以握。不可以定。昔者成连见海波之汹涌而悟琴之道。成连固如此矣。假令复有人慕成连之事。而抱琴更立于海波汹涌之际。则当何如哉。夫成连之悟。乃屡年深思之力之所为。而非一朝之间无故而致者。故与其劝人以悟。毋宁劝人以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慕道术文章。不如仰而一思。善乎晋州河子信之为文也。子信为文几年。自谓无所媮快。益加精思。取古人漱六艺之芳润之语。而署其所居藏书万卷之室曰漱润堂。夫芳者物之腐。臭之反也。润者物之枯。暗之反也。芳积于中然后。润著于外。故言润则芳在其中矣。漱其润于口。则口之洁养可知矣。夫以吾之一心。而沉浸反覆于六艺。犹口之漱润。岂非心之思之至乎。前修之言曰。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吾知子信坐是堂读是书。一日之顷。豁然大悟。去腐臭而就芳。去枯暗而就润。如雷霆之轰轰然起蛰也不远矣。远思斋记(己未)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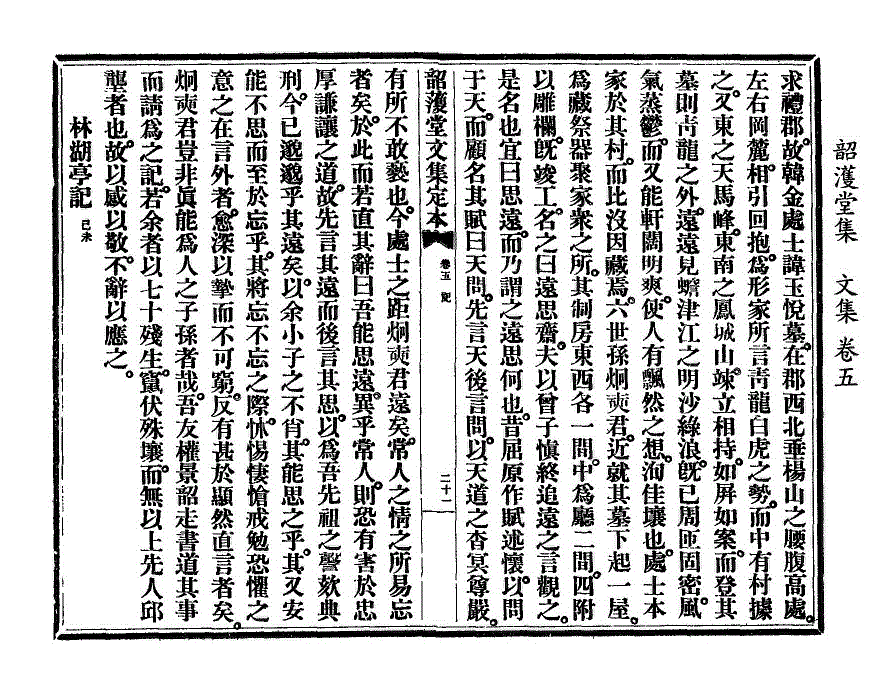 求礼郡。故韩金处士讳玉悦墓。在郡西北垂杨山之腰腹高处。左右冈麓。相引回抱。为形家所言青龙白虎之势。而中有村据之。又东之天马峰。东南之凤城山。竦立相持。如屏如案。而登其墓则青龙之外。远远见蟾津江之明沙绿浪。既已周匝固密。风气蒸郁。而又能轩阔明爽。使人有飘然之想。洵佳壤也。处士本家于其村。而比没因藏焉。六世孙炯奭君。近就其墓下起一屋。为藏祭器聚家众之所。其制房东西各一间。中为厅二间。四附以雕栏。既竣工。名之曰远思斋。夫以曾子慎终追远之言观之。是名也宜曰思远。而乃谓之远思何也。昔屈原作赋述怀。以问于天。而顾名其赋曰天问。先言天后言问。以天道之杳冥尊严。有所不敢亵也。今处士之距炯奭君远矣。常人之情之所易忘者矣。于此而若直其辞曰吾能思远。异乎常人。则恐有害于忠厚谦让之道。故先言其远而后言其思。以为吾先祖之謦欬典刑。今已邈邈乎其远矣。以余小子之不肖。其能思之乎。其又安能不思而至于忘乎。其将忘不忘之际。怵惕悽怆戒勉恐惧之意之在言外者。愈深以挚而不可穷。反有甚于显然直言者矣。炯奭君岂非真能为人之子孙者哉。吾友权景韶走书道其事而请为之记。若余者以七十残生。窜伏殊壤。而无以上先人邱垄者也。故以感以敬。不辞以应之。
求礼郡。故韩金处士讳玉悦墓。在郡西北垂杨山之腰腹高处。左右冈麓。相引回抱。为形家所言青龙白虎之势。而中有村据之。又东之天马峰。东南之凤城山。竦立相持。如屏如案。而登其墓则青龙之外。远远见蟾津江之明沙绿浪。既已周匝固密。风气蒸郁。而又能轩阔明爽。使人有飘然之想。洵佳壤也。处士本家于其村。而比没因藏焉。六世孙炯奭君。近就其墓下起一屋。为藏祭器聚家众之所。其制房东西各一间。中为厅二间。四附以雕栏。既竣工。名之曰远思斋。夫以曾子慎终追远之言观之。是名也宜曰思远。而乃谓之远思何也。昔屈原作赋述怀。以问于天。而顾名其赋曰天问。先言天后言问。以天道之杳冥尊严。有所不敢亵也。今处士之距炯奭君远矣。常人之情之所易忘者矣。于此而若直其辞曰吾能思远。异乎常人。则恐有害于忠厚谦让之道。故先言其远而后言其思。以为吾先祖之謦欬典刑。今已邈邈乎其远矣。以余小子之不肖。其能思之乎。其又安能不思而至于忘乎。其将忘不忘之际。怵惕悽怆戒勉恐惧之意之在言外者。愈深以挚而不可穷。反有甚于显然直言者矣。炯奭君岂非真能为人之子孙者哉。吾友权景韶走书道其事而请为之记。若余者以七十残生。窜伏殊壤。而无以上先人邱垄者也。故以感以敬。不辞以应之。林湖亭记(己未)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五 第 290L 页
 故韩议官陜川李君灏燮走书问交。请记其大人湖帆处士所置之林湖亭。仍示处士所作亭之杂咏。盖亭在巢鹤山之南锦江之北林湖村之傍。本姜氏物。处士买而修之。以所居之村名署之。因以品题十有九之景槩。欲于朝夕之间。偃仰陟降。眺瞩漱濯。极江山烟云风月花竹之赏玩。以忘故宗国风泉黍离之悲而终其残年。其罔仆自靖之义。可谓至矣。噫。余虽未睹所谓十有九之景槩。窃自因风而思念之。其地在辰韩则岂不曰是吾辰韩之所有乎。在新罗则岂不曰是吾新罗之所有乎。在高丽及我韩则岂不曰是吾高丽韩之所有乎。其有之之道。又岂皆非英雄俊杰之经营。智臣勇将之先后。铦戟利剑之擉斫。坚城险堡之防捍乎。然而一朝运去。则迭为他人所有而以至于今日。又再思之。则今日之有者。亦将有时而复视乎前人。如空云海沤之递相起灭而已。若处士之所以有者。罔仆自靖之义也。虽其所以为先后防捍者。不过乎弱子羸仆短垣疏樊。而其义也孰得而灭诸。夫同一地而所有之不同如此。故余太息而一论之。使处士益自信其义。而亦使天下后世知人之国家虽亡于奸臣逆子。而君子之道未尝亡也。处士名相翼。
故韩议官陜川李君灏燮走书问交。请记其大人湖帆处士所置之林湖亭。仍示处士所作亭之杂咏。盖亭在巢鹤山之南锦江之北林湖村之傍。本姜氏物。处士买而修之。以所居之村名署之。因以品题十有九之景槩。欲于朝夕之间。偃仰陟降。眺瞩漱濯。极江山烟云风月花竹之赏玩。以忘故宗国风泉黍离之悲而终其残年。其罔仆自靖之义。可谓至矣。噫。余虽未睹所谓十有九之景槩。窃自因风而思念之。其地在辰韩则岂不曰是吾辰韩之所有乎。在新罗则岂不曰是吾新罗之所有乎。在高丽及我韩则岂不曰是吾高丽韩之所有乎。其有之之道。又岂皆非英雄俊杰之经营。智臣勇将之先后。铦戟利剑之擉斫。坚城险堡之防捍乎。然而一朝运去。则迭为他人所有而以至于今日。又再思之。则今日之有者。亦将有时而复视乎前人。如空云海沤之递相起灭而已。若处士之所以有者。罔仆自靖之义也。虽其所以为先后防捍者。不过乎弱子羸仆短垣疏樊。而其义也孰得而灭诸。夫同一地而所有之不同如此。故余太息而一论之。使处士益自信其义。而亦使天下后世知人之国家虽亡于奸臣逆子。而君子之道未尝亡也。处士名相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