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x 页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序
序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6H 页
 开城家稿序(壬子)
开城家稿序(壬子)余少时游三南。以姜秋琴翁富于游览。就问三南山川人士。秋琴翁曰。子至智异山。将访豪士。则其求礼王素琴。为高丽太祖之苗裔者乎。余果如其言访之。后三十馀年。素琴访余于汉京宦寓。则须发两皆苍然。相视而叹。又未几而闻素琴之卒逝。宁不悲哉。近为亡友黄梅泉。驰书于其门人及从游者。劝刊其诗。于是其从游之翘。有王云樵者。慨然首奋。克集其事。而以书报余。辞旨芬激。即素琴兄凤洲之子也。余为之叹曰。何王氏之多贤。而余之所遇。又多在于王氏也。一日云樵送其家稿徵序。在卷之首者曰川社先生。其三子凤洲,素琴,小川。以次从之。而小川年今六十馀。独存于世矣。噫。凡此四君子者。皆有才而遗逸牢骚者耳。然当吾韩升平之日。父子兄弟之间。弓之箕之。埙之篪之。以自乐于智异鹑江之间。而续邵尧夫击壤之什者。何其盛矣。今则所谓智异之山。鹑江之水。孰为之高而孰为之清也。抑素琴子之飘然奉陪父兄先生于冥茫之中尘埃之表。遗弃世事如脱屣。无复所谓兴亡得失悲欢苦乐者。幸耶非耶。小川翁闻此。其将因风太息。而益发为不平之诗矣乎。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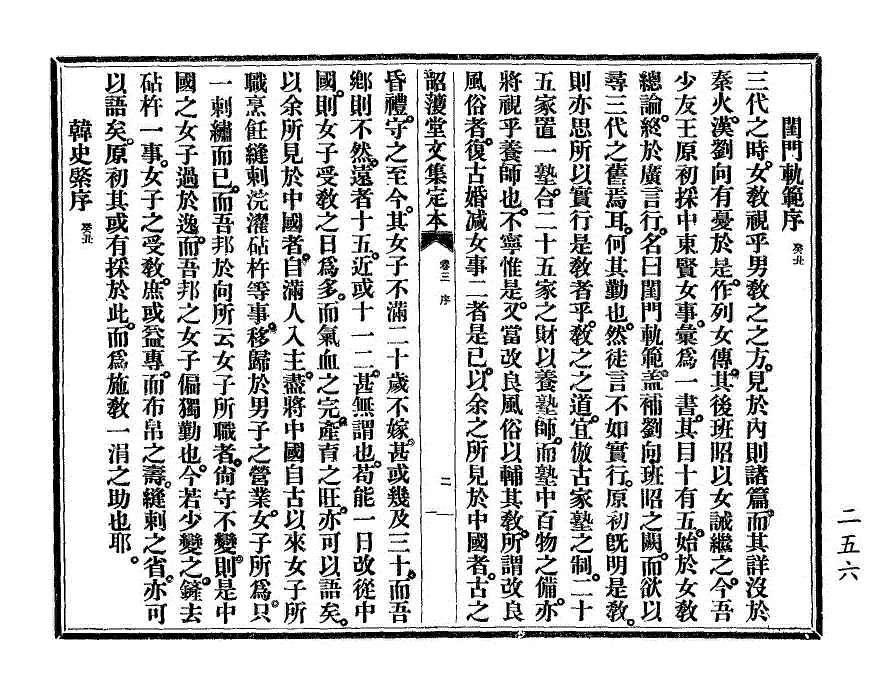 闺门轨范序(癸丑)
闺门轨范序(癸丑)三代之时。女教视乎男教之之方。见于内则诸篇。而其详没于秦火。汉刘向有忧于是。作列女传。其后班昭以女诫继之。今吾少友王原初采中东贤女事。汇为一书。其目十有五。始于女教总论。终于广言行。名曰闺门轨范。盖补刘向,班昭之阙。而欲以寻三代之旧焉耳。何其勤也。然徒言不如实行。原初既明是教。则亦思所以实行是教者乎。教之之道。宜仿古家塾之制。二十五家置一塾。合二十五家之财以养塾师。而塾中百物之备。亦将视乎养师也。不宁惟是。又当改良风俗以辅其教。所谓改良风俗者。复古婚减女事二者是已。以余之所见于中国者。古之昏礼。守之至今。其女子不满二十岁不嫁。甚或几及三十。而吾乡则不然。远者十五。近或十一二。甚无谓也。苟能一日改从中国。则女子受教之日为多。而气血之完。产育之旺。亦可以语矣。以余所见于中国者。自满人入主。尽将中国自古以来女子所职烹饪缝刺浣濯砧杵等事。移归于男子之营业。女子所为。只一刺绣而已。而吾邦于向所云女子所职者。尚守不变。则是中国之女子过于逸。而吾邦之女子偏独勤也。今若少变之。铲去砧杵一事。女子之受教。庶或益专。而布帛之寿。缝刺之省。亦可以语矣。原初其或有采于此。而为施教一涓之助也耶。
韩史綮序(癸丑)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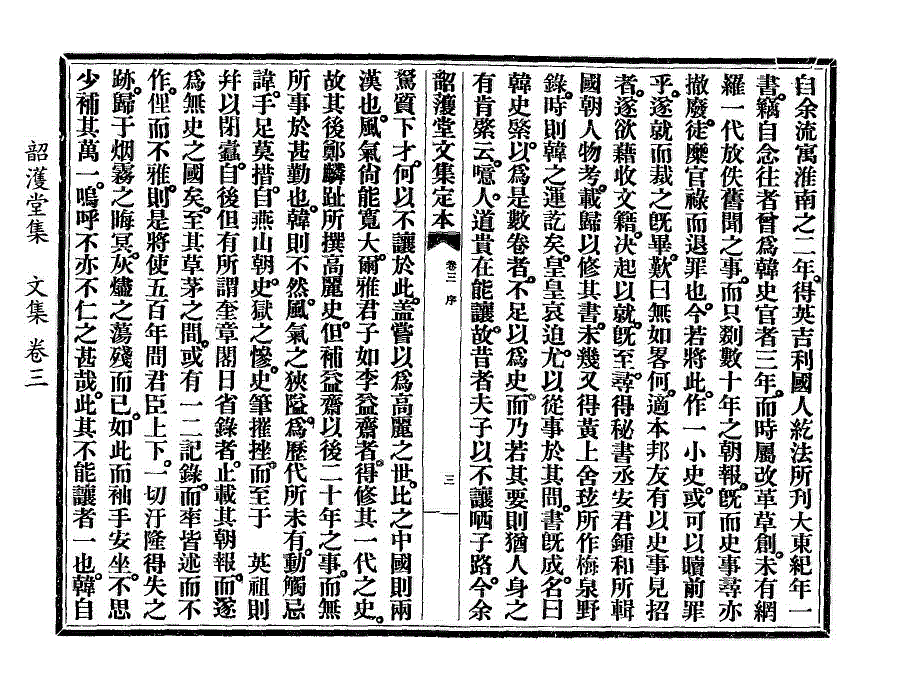 自余流寓淮南之二年。得英吉利国人纥法所刊大东纪年一书。窃自念往者曾为韩史官者三年。而时属改革草创。未有网罗一代放佚旧闻之事。而只剟数十年之朝报。既而史事寻亦撤废。徒糜官禄而退罪也。今若将此。作一小史。或可以赎前罪乎。遂就而裁之既毕。叹曰无如略何。适本邦友有以史事见招者。遂欲藉收文籍。决起以就。既至。寻得秘书丞安君钟和所辑国朝人物考。载归以修其书。未几又得黄上舍玹所作梅泉野录。时则韩之运讫矣。皇皇哀迫。尤以从事于其间。书既成。名曰韩史綮。以为是数卷者。不足以为史。而乃若其要则犹人身之有肯綮云。噫。人道贵在能让。故昔者夫子以不让哂子路。今余驽质下才。何以不让于此。盖尝以为高丽之世。比之中国则两汉也。风气尚能宽大。尔雅君子如李益斋者。得修其一代之史。故其后郑麟趾所撰高丽史。但补益斋以后二十年之事。而无所事于甚勤也。韩则不然。风气之狭隘。为历代所未有。动触忌讳。手足莫措。自燕山朝。史狱之惨。史笔摧挫。而至于 英祖则并以闭蠹。自后但有所谓奎章阁日省录者。止载其朝报。而遂为无史之国矣。至其草茅之间。或有一二记录。而率皆述而不作。俚而不雅。则是将使五百年间君臣上下。一切污隆得失之迹。归于烟雾之晦冥。灰烬之荡残而已。如此而袖手安坐。不思少补其万一。呜呼不亦不仁之甚哉。此其不能让者一也。韩自
自余流寓淮南之二年。得英吉利国人纥法所刊大东纪年一书。窃自念往者曾为韩史官者三年。而时属改革草创。未有网罗一代放佚旧闻之事。而只剟数十年之朝报。既而史事寻亦撤废。徒糜官禄而退罪也。今若将此。作一小史。或可以赎前罪乎。遂就而裁之既毕。叹曰无如略何。适本邦友有以史事见招者。遂欲藉收文籍。决起以就。既至。寻得秘书丞安君钟和所辑国朝人物考。载归以修其书。未几又得黄上舍玹所作梅泉野录。时则韩之运讫矣。皇皇哀迫。尤以从事于其间。书既成。名曰韩史綮。以为是数卷者。不足以为史。而乃若其要则犹人身之有肯綮云。噫。人道贵在能让。故昔者夫子以不让哂子路。今余驽质下才。何以不让于此。盖尝以为高丽之世。比之中国则两汉也。风气尚能宽大。尔雅君子如李益斋者。得修其一代之史。故其后郑麟趾所撰高丽史。但补益斋以后二十年之事。而无所事于甚勤也。韩则不然。风气之狭隘。为历代所未有。动触忌讳。手足莫措。自燕山朝。史狱之惨。史笔摧挫。而至于 英祖则并以闭蠹。自后但有所谓奎章阁日省录者。止载其朝报。而遂为无史之国矣。至其草茅之间。或有一二记录。而率皆述而不作。俚而不雅。则是将使五百年间君臣上下。一切污隆得失之迹。归于烟雾之晦冥。灰烬之荡残而已。如此而袖手安坐。不思少补其万一。呜呼不亦不仁之甚哉。此其不能让者一也。韩自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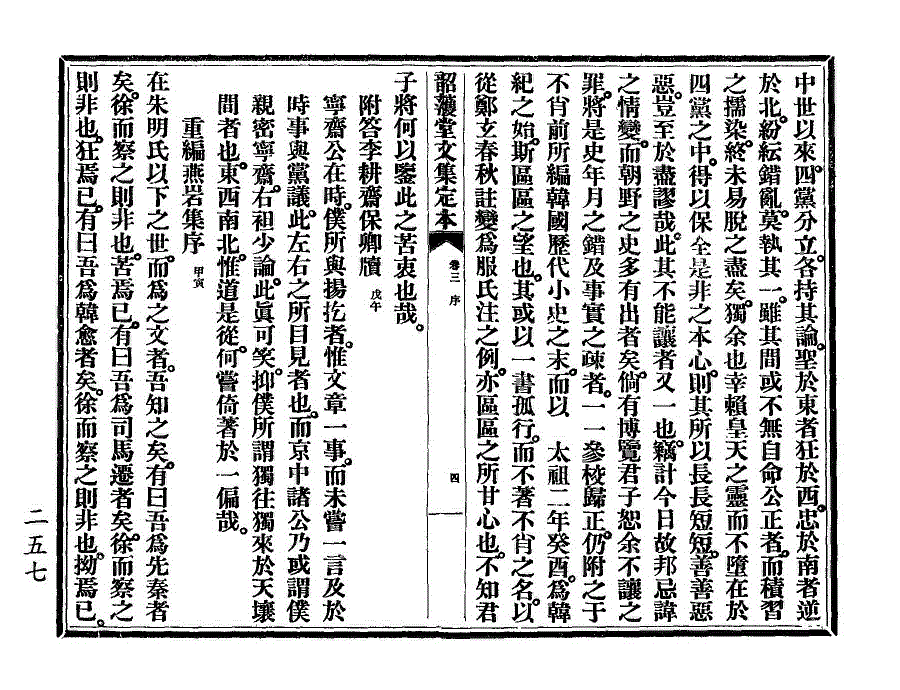 中世以来。四党分立。各持其论。圣于东者狂于西。忠于南者逆于北。纷纭错乱。莫执其一。虽其间或不无自命公正者。而积习之擩染。终未易脱之尽矣。独余也幸赖皇天之灵而不堕在于四党之中。得以保全是非之本心。则其所以长长短短。善善恶恶。岂至于尽谬哉。此其不能让者又一也。窃计今日故邦忌讳之情变。而朝野之史多有出者矣。倘有博览君子恕余不让之罪。将是史年月之错及事实之疏者。一一参校归正。仍附之于不肖前所编韩国历代小史之末。而以 太祖二年癸酉。为韩纪之始。斯区区之望也。其或以一书孤行。而不著不肖之名。以从郑玄春秋注变为服氏注之例。亦区区之所甘心也。不知君子将何以鉴此之苦衷也哉。
中世以来。四党分立。各持其论。圣于东者狂于西。忠于南者逆于北。纷纭错乱。莫执其一。虽其间或不无自命公正者。而积习之擩染。终未易脱之尽矣。独余也幸赖皇天之灵而不堕在于四党之中。得以保全是非之本心。则其所以长长短短。善善恶恶。岂至于尽谬哉。此其不能让者又一也。窃计今日故邦忌讳之情变。而朝野之史多有出者矣。倘有博览君子恕余不让之罪。将是史年月之错及事实之疏者。一一参校归正。仍附之于不肖前所编韩国历代小史之末。而以 太祖二年癸酉。为韩纪之始。斯区区之望也。其或以一书孤行。而不著不肖之名。以从郑玄春秋注变为服氏注之例。亦区区之所甘心也。不知君子将何以鉴此之苦衷也哉。附答李耕斋保卿牍(戊午)
宁斋公在时。仆所与扬扢者。惟文章一事。而未尝一言及于时事与党议。此左右之所目见者也。而京中诸公乃或谓仆亲密宁斋。右袒少论。此真可笑。抑仆所谓独往独来于天壤间者也。东西南北。惟道是从。何尝倚著于一偏哉。
重编燕岩集序(甲寅)
在朱明氏以下之世。而为之文者。吾知之矣。有曰吾为先秦者矣。徐而察之则非也。苦焉已。有曰吾为司马迁者矣。徐而察之则非也。狂焉已。有曰吾为韩愈者矣。徐而察之则非也。拗焉已。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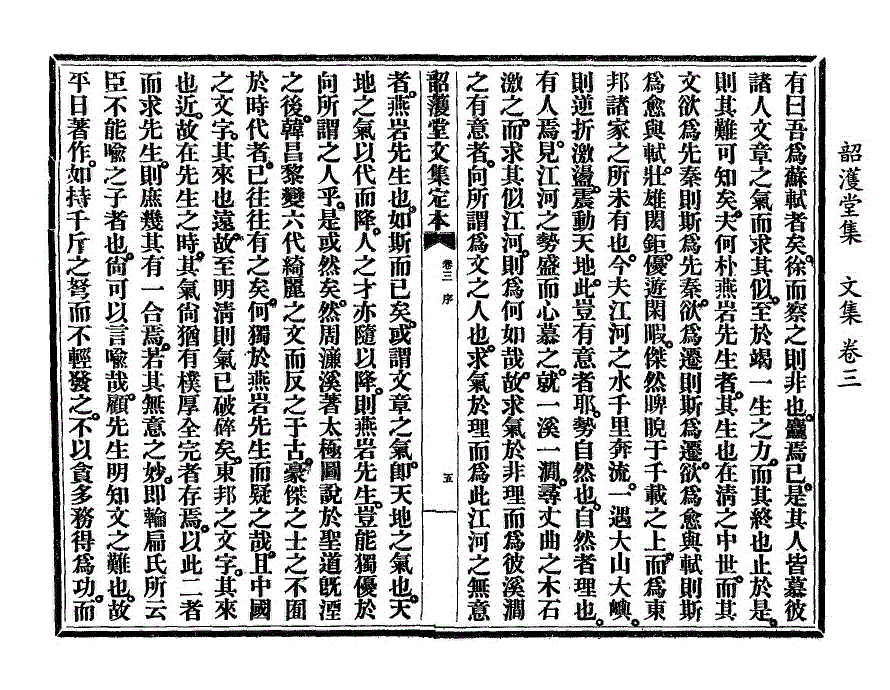 有曰吾为苏轼者矣。徐而察之则非也。粗焉已。是其人皆慕彼诸人文章之气而求其似。至于竭一生之力。而其终也止于是。则其难可知矣。夫何朴燕岩先生者。其生也在清之中世。而其文欲为先秦则斯为先秦。欲为迁则斯为迁。欲为愈与轼则斯为愈与轼。壮雄闳钜。优游闲暇。杰然睥睨于千载之上。而为东邦诸家之所未有也。今夫江河之水千里奔流。一遇大山大屿。则逆折激荡。震动天地。此岂有意者耶。势自然也。自然者理也。有人焉。见江河之势盛而心慕之。就一溪一涧。寻丈曲之木石激之。而求其似江河。则为何如哉。故求气于非理而为彼溪涧之有意者。向所谓为文之人也。求气于理而为此江河之无意者。燕岩先生也。如斯而已矣。或谓文章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天地之气以代而降。人之才亦随以降。则燕岩先生。岂能独优于向所谓之人乎。是或然矣。然周濂溪著太极图说于圣道既湮之后。韩昌黎变六代绮丽之文而反之于古。豪杰之士之不囿于时代者。已往往有之矣。何独于燕岩先生而疑之哉。且中国之文字。其来也远。故至明清则气已破碎矣。东邦之文字。其来也近。故在先生之时。其气尚犹有朴厚全完者存焉。以此二者而求先生。则庶几其有一合焉。若其无意之妙。即轮扁氏所云臣不能喻之子者也。尚可以言喻哉。顾先生明知文之难也。故平日著作。如持千斤之弩而不轻发之。不以贪多务得为功。而
有曰吾为苏轼者矣。徐而察之则非也。粗焉已。是其人皆慕彼诸人文章之气而求其似。至于竭一生之力。而其终也止于是。则其难可知矣。夫何朴燕岩先生者。其生也在清之中世。而其文欲为先秦则斯为先秦。欲为迁则斯为迁。欲为愈与轼则斯为愈与轼。壮雄闳钜。优游闲暇。杰然睥睨于千载之上。而为东邦诸家之所未有也。今夫江河之水千里奔流。一遇大山大屿。则逆折激荡。震动天地。此岂有意者耶。势自然也。自然者理也。有人焉。见江河之势盛而心慕之。就一溪一涧。寻丈曲之木石激之。而求其似江河。则为何如哉。故求气于非理而为彼溪涧之有意者。向所谓为文之人也。求气于理而为此江河之无意者。燕岩先生也。如斯而已矣。或谓文章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天地之气以代而降。人之才亦随以降。则燕岩先生。岂能独优于向所谓之人乎。是或然矣。然周濂溪著太极图说于圣道既湮之后。韩昌黎变六代绮丽之文而反之于古。豪杰之士之不囿于时代者。已往往有之矣。何独于燕岩先生而疑之哉。且中国之文字。其来也远。故至明清则气已破碎矣。东邦之文字。其来也近。故在先生之时。其气尚犹有朴厚全完者存焉。以此二者而求先生。则庶几其有一合焉。若其无意之妙。即轮扁氏所云臣不能喻之子者也。尚可以言喻哉。顾先生明知文之难也。故平日著作。如持千斤之弩而不轻发之。不以贪多务得为功。而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8L 页
 乃后之人。或妄相以先生所弃者而猥入之。欲以誇富。则是大伤先生之意也。岂非过哉。是以余于先生之文。既删减为原续二集。后又合二集为一。而再删为七卷。以见其文之愈少愈贵者。为合于先生之本意也。求礼金君士元闻而然之。踊跃图刊。君即吾亡友黄云卿之徒。而为能大异于时俗梦梦者也。故辄感动于中而为之言。
乃后之人。或妄相以先生所弃者而猥入之。欲以誇富。则是大伤先生之意也。岂非过哉。是以余于先生之文。既删减为原续二集。后又合二集为一。而再删为七卷。以见其文之愈少愈贵者。为合于先生之本意也。求礼金君士元闻而然之。踊跃图刊。君即吾亡友黄云卿之徒。而为能大异于时俗梦梦者也。故辄感动于中而为之言。张季子诗录序(甲寅)
泽荣东韩之窾民也。何足以知张啬庵先生。虽然获交先生三十年之中。为邦运所迫而来依于南通者十年矣。论说之与久。耳目之与迩。其一二所知。宁敢独后于天下之士大夫也。则题其诗录之卷首曰。古之所谓大人天民者。其气也庞。其心也正。其志也大而忧。其发于文章也平而实。而其施于事业也。为济世安民。自皋陶伊傅。以至韩琦,范仲淹诸人是已。其不及此者。其气也峭。其心也偏。其志也小而荡。其发于文章也奇而虚。而其施于事业也。且不能济其三族。自庄周,太史公。以至李白,杜甫诸人是已。譬诸物。前之人犹布帛菽粟也。后之人犹奇花异卉也。人无奇花异卉。未始不可生。而无布帛菽粟。则可以生乎。然则之二人者之度量浅深可知。而天下古今之论人。可以此一言而盖之矣乎。先生生有通才伟量。自其少为秀才时。已能隐蓄天下之奇志。及夫中岁释褐以来。见中国积萎侮于列强。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9H 页
 数上书当事大僚。陈政治利害得失之大要。卒不见采。乃绝断进取。俦伍农商。遂资实业。私建学校。以瀹民智育人才。为其标的。又推其馀力。以及于公益慈善之事者。不可胜数。于以日夜憧憧。形神俱瘁者十馀年。既而中国之形变为共和。则迫于天下之公议而出焉。方将开诚布公。剔神抉智。日施其畎亩之所素定者。虽其事业之所极。今不可预言。而其所以一心忧民。好行善事。直与范文正公符契相合于千载之间。岂不盛哉。先生近属门人束曰琯,李祯二君。综其著作。为政事录,教育录,实业录,慈善录,政治录,杂文录,诗录七类既讫。二君请刊自诗录。先生笑而从之。噫。今之中国。即自剥进复之会也。阴阳消长之危机。间不容发。上下大小。方且皇皇汲汲。求其自治。则其于先生之文字。所愿先睹以为快者。必在于政事慈善诸录。而诗非其急也。然先生之文章。本自平实清刚。不涉虚荡而诗为尤然。一读可知其为救世安民有德者之言。而不止为风雅正宗而已。世之知慕先生者。请姑先读是诗。而待诸录之朝暮出也哉。中华民国三年旧历甲寅闰五月。同县新民韩产金泽荣序。
数上书当事大僚。陈政治利害得失之大要。卒不见采。乃绝断进取。俦伍农商。遂资实业。私建学校。以瀹民智育人才。为其标的。又推其馀力。以及于公益慈善之事者。不可胜数。于以日夜憧憧。形神俱瘁者十馀年。既而中国之形变为共和。则迫于天下之公议而出焉。方将开诚布公。剔神抉智。日施其畎亩之所素定者。虽其事业之所极。今不可预言。而其所以一心忧民。好行善事。直与范文正公符契相合于千载之间。岂不盛哉。先生近属门人束曰琯,李祯二君。综其著作。为政事录,教育录,实业录,慈善录,政治录,杂文录,诗录七类既讫。二君请刊自诗录。先生笑而从之。噫。今之中国。即自剥进复之会也。阴阳消长之危机。间不容发。上下大小。方且皇皇汲汲。求其自治。则其于先生之文字。所愿先睹以为快者。必在于政事慈善诸录。而诗非其急也。然先生之文章。本自平实清刚。不涉虚荡而诗为尤然。一读可知其为救世安民有德者之言。而不止为风雅正宗而已。世之知慕先生者。请姑先读是诗。而待诸录之朝暮出也哉。中华民国三年旧历甲寅闰五月。同县新民韩产金泽荣序。杨谷孙文卷序(甲寅)
杨君谷孙为童子师。取其用力之当。以养偏母。以其暇治古文辞。凡世间一切芬华枯槁。丰盈匮缺。屈辱伸荣之可悲可忧者。皆不入之心。而惟心之于文焉。每作一篇。意有所未快。则质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59L 页
 于朋曹。质于朋曹而犹未快。则质之于乡先生。质于乡先生而犹未快。则至及于如余亡国之馀贱秽之品而不之已。此岂流俗之间。骄吝褊私。龌龊者之所敢望哉。独念君读天下书多矣。出入乎古人文章之论议已久矣。何乃尚蹙蹙焉不自安乎。以余所阅。余少时才质甚愚。且又乡居无师。所习不过乎科举之学。一日忽自慨念文字之道。当不止是。取旧书更读之。则前日所自谓知者。乃反皆不可知而梦梦矣。时或注之手。则戛戛乎其不可续矣。于是大忧之。日夜思绎。不敢暂宁。凡古之名流及同时畏友之所系乎慕者。宵梦与接。岁不下数十。及弱冠。西游箕子故都。览其江山胜丽。因又东放于沙海。以穷万里之波涛。既归。得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砉然开解。自是以往。向之所梦梦者。始渐可以有知。向之所戛戛者。始渐可以畅注。此余之所以自快也。抑余之所以自快者。自君观之。又安知非其尚未快者耶。然徐而思之。归氏之文。岂能独感余哉。特余之所感触者。偶在于是。而其所以感触之妙。又在于思之笃。盖思而后感。感而后通。通而后快。此其序之不可易者。君不能以独异于我也。故兹就君之文。录书之如右。所以厚望之也。虽然君之贤于流俗既甚远。则是固道德之符而之贤哲之涂也。藉令君之文。有不能如吾之所望者。君其何病之有。
于朋曹。质于朋曹而犹未快。则质之于乡先生。质于乡先生而犹未快。则至及于如余亡国之馀贱秽之品而不之已。此岂流俗之间。骄吝褊私。龌龊者之所敢望哉。独念君读天下书多矣。出入乎古人文章之论议已久矣。何乃尚蹙蹙焉不自安乎。以余所阅。余少时才质甚愚。且又乡居无师。所习不过乎科举之学。一日忽自慨念文字之道。当不止是。取旧书更读之。则前日所自谓知者。乃反皆不可知而梦梦矣。时或注之手。则戛戛乎其不可续矣。于是大忧之。日夜思绎。不敢暂宁。凡古之名流及同时畏友之所系乎慕者。宵梦与接。岁不下数十。及弱冠。西游箕子故都。览其江山胜丽。因又东放于沙海。以穷万里之波涛。既归。得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砉然开解。自是以往。向之所梦梦者。始渐可以有知。向之所戛戛者。始渐可以畅注。此余之所以自快也。抑余之所以自快者。自君观之。又安知非其尚未快者耶。然徐而思之。归氏之文。岂能独感余哉。特余之所感触者。偶在于是。而其所以感触之妙。又在于思之笃。盖思而后感。感而后通。通而后快。此其序之不可易者。君不能以独异于我也。故兹就君之文。录书之如右。所以厚望之也。虽然君之贤于流俗既甚远。则是固道德之符而之贤哲之涂也。藉令君之文。有不能如吾之所望者。君其何病之有。困言序(乙卯)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0H 页
 天能与人五性。而不能教之使勿失其性。惟圣哲先觉之人。明五性所赋之源以教人。使其失者得以复之。其功也并乎天。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拒杨墨。程朱氏之辟佛。皆是已。自外人之扰内。内之被其害者。动心丧魄。惴惴焉恐吾之人类将尽刘。日夜逐逐学外。如恐不及。虽平日粗读圣人之籍者。亦靡然摧折而与之俱往。吾友深斋曹子。独毅然不改其守。取困卦有言不信之词。作困言一编。以明其性。思有以继孔孟程朱之遗规。其心可谓苦矣。然世俗之辁士。若读而迂之。以为干戚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围。则深斋子之志。将无以达于天下。而其功也阏矣。愚请有以明之。天下之常情。安于内而惊于外。易于常而难于怪。而不知性之本善与迪逆之吉凶内外彼此一也。姑以内事言之。昔者蚩尤铜铁其额。能作大雾。而黄帝歼之。则其性明焉。商纣刳妇腹视其胎。而武王诛之。则其性明焉。项羽坑降卒二十万。而汉高帝克之。则其性明焉。此申包胥所谓天定胜人也。夫彼作雾刳腹坑降。一切乱神凶残之所为。岂不浮于今之外人。而犹且以天胜之。况于外人乎。何忧胜之之无日。而乃自贱其性。恇怯颓堕。反以深斋子为疑哉。深斋子数年前作一论。极言孔子事君之大义。以惜中国新制之失。今也中国果病于新。而议复其旧。是则孔子明见万世。而深斋子能逆睹数年之外尔。世之人其亦以此为鉴。尊信此书而有以复其性也哉。
天能与人五性。而不能教之使勿失其性。惟圣哲先觉之人。明五性所赋之源以教人。使其失者得以复之。其功也并乎天。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拒杨墨。程朱氏之辟佛。皆是已。自外人之扰内。内之被其害者。动心丧魄。惴惴焉恐吾之人类将尽刘。日夜逐逐学外。如恐不及。虽平日粗读圣人之籍者。亦靡然摧折而与之俱往。吾友深斋曹子。独毅然不改其守。取困卦有言不信之词。作困言一编。以明其性。思有以继孔孟程朱之遗规。其心可谓苦矣。然世俗之辁士。若读而迂之。以为干戚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围。则深斋子之志。将无以达于天下。而其功也阏矣。愚请有以明之。天下之常情。安于内而惊于外。易于常而难于怪。而不知性之本善与迪逆之吉凶内外彼此一也。姑以内事言之。昔者蚩尤铜铁其额。能作大雾。而黄帝歼之。则其性明焉。商纣刳妇腹视其胎。而武王诛之。则其性明焉。项羽坑降卒二十万。而汉高帝克之。则其性明焉。此申包胥所谓天定胜人也。夫彼作雾刳腹坑降。一切乱神凶残之所为。岂不浮于今之外人。而犹且以天胜之。况于外人乎。何忧胜之之无日。而乃自贱其性。恇怯颓堕。反以深斋子为疑哉。深斋子数年前作一论。极言孔子事君之大义。以惜中国新制之失。今也中国果病于新。而议复其旧。是则孔子明见万世。而深斋子能逆睹数年之外尔。世之人其亦以此为鉴。尊信此书而有以复其性也哉。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0L 页
 守庵稿序(丙辰)
守庵稿序(丙辰)往在故韩 太上皇甲戌。余于李宁斋学士席上。见守庵子。学士为余媒其交曰。此岭南名士李韦史也。韦史者守庵子之别称也。其秋守庵子访余开城。余导游天磨山。相与赋诗于七星庵中。自是入都。未尝不与之相会。见其场屋对策。与三嘉朴晚醒争雄。一时应书之士。莫不以沾丐馀膏为幸。顾其胸中所自期。在于王元美,李于鳞一流人之文。而不止于功令。何其奇矣。自壬午兵变之后。守庵子归乡杜门。一日宁斋惨然向余语曰。韦史厄死矣。因出示所作秋水子传。秋水子者。讳其所以死。摘其平日所为诗之语。以隐称之者也。后三十馀年。其从子柱鲁及族孙光世。相与综其诗文。将刊之。谓余宜有一序。嗟乎。宁斋学士。今亦已没矣。不知所谓秋水子传者。已能致之于守庵子之家。而使之得列于其遗稿否。俛仰今昔。忽不觉古人车过腹痛之语之自出于口矣。然迹守庵子遭厄之故。盖欲行其志而措国家于安泰也。使其志得行。安有国家今日之不幸。而志既不可行。则毋宁先国家而死灭。不见今日之不幸。尚何其死之足吊也。愿读其稿者。与韩非说难,杜牧罪言,杜甫北征诗之类而并读之。以考其志而论其世也哉。
后隐文翁六十三岁寿序(丙辰)
始余因曹处士仲谨。识文君永朴章之。窃覸章之所行。有国士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1H 页
 风。为之心服。间以语及于仲谨。仲谨曰。惜子未见其大人后隐翁。章之之所为。皆翁之教也。翁之生为甲寅十月十三日。而回甲之春。适罹母服。章之不能称寿。至是将补设寿宴。仲谨以章之意劝祝翁。因加述翁之平生。盖翁为人宽厚闳豁。少治生产。以勤致腴。中年以后。不复握算求益。贬其自奉而布施之。凡穷亲贫友之得其赖者。不可胜数。性绝好文学。遇有鸿儒硕士。必极隆其礼遇。以及傍郡人客之游过者。苟能粗知文字。必留而衣食之。动逾岁月无苦色。而其子孙众多。以至于曾孙。门庭之间。和气蔼然。于是人莫不贤翁。而尤啧啧称其福。然观于史传。翁之先祖忠宣公。当高丽季世。以大忠大孝。为人所称。然位不能称之。而其终也。又以遗民没其齿。且又闻之。仲谨忠宣之后。以布衣行仁义于丘里之中者。亦复不少。则可谓之积累之久远。而翁以若彼之茂行承之。夫积于植则为松柏之茂。积于凿则为井泉之冽。故范文正公有云自吾祖宗积德百馀年。始发于吾。由此言之。翁之世德之积累者。且将大发于翁而震惊一世矣。何止于子孙众多之福而已哉。称觞之日。吾且将遥沥酒于海天之东。诵范公之言而为诸祝者之前行矣。
风。为之心服。间以语及于仲谨。仲谨曰。惜子未见其大人后隐翁。章之之所为。皆翁之教也。翁之生为甲寅十月十三日。而回甲之春。适罹母服。章之不能称寿。至是将补设寿宴。仲谨以章之意劝祝翁。因加述翁之平生。盖翁为人宽厚闳豁。少治生产。以勤致腴。中年以后。不复握算求益。贬其自奉而布施之。凡穷亲贫友之得其赖者。不可胜数。性绝好文学。遇有鸿儒硕士。必极隆其礼遇。以及傍郡人客之游过者。苟能粗知文字。必留而衣食之。动逾岁月无苦色。而其子孙众多。以至于曾孙。门庭之间。和气蔼然。于是人莫不贤翁。而尤啧啧称其福。然观于史传。翁之先祖忠宣公。当高丽季世。以大忠大孝。为人所称。然位不能称之。而其终也。又以遗民没其齿。且又闻之。仲谨忠宣之后。以布衣行仁义于丘里之中者。亦复不少。则可谓之积累之久远。而翁以若彼之茂行承之。夫积于植则为松柏之茂。积于凿则为井泉之冽。故范文正公有云自吾祖宗积德百馀年。始发于吾。由此言之。翁之世德之积累者。且将大发于翁而震惊一世矣。何止于子孙众多之福而已哉。称觞之日。吾且将遥沥酒于海天之东。诵范公之言而为诸祝者之前行矣。周晋琦诗稿序(丙辰)
往在前清道光,咸丰之间。前辈文章钜公。悯其时声诗之佻轻。略效宋黄鲁直之诗体以救之。则其诗固尝清健奇豪矣。其流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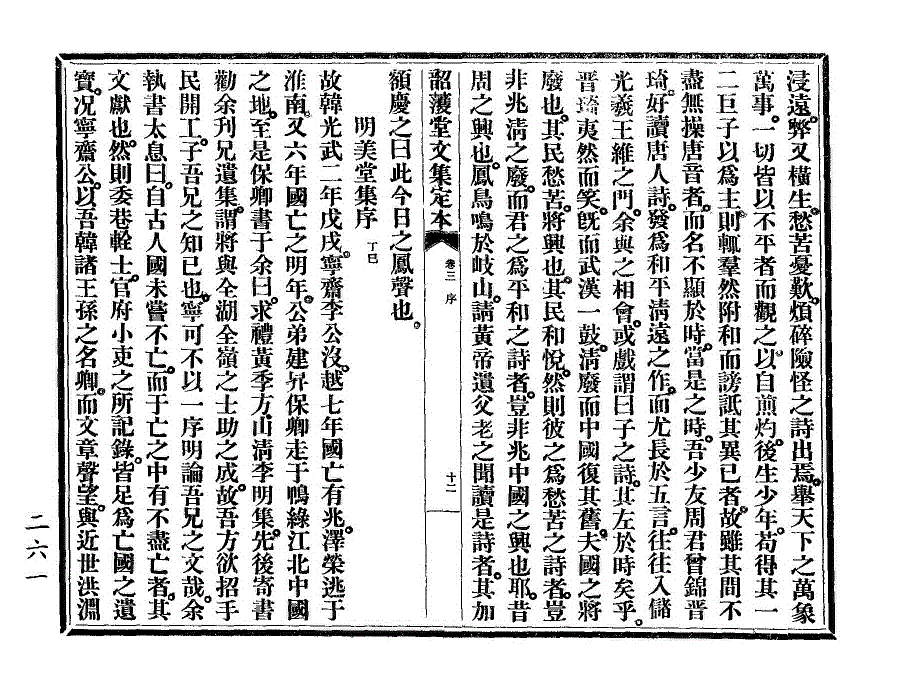 浸远。弊又横生。愁苦忧叹。烦碎险怪之诗出焉。举天下之万象万事。一切皆以不平者而观之。以自煎灼。后生少年。苟得其一二巨子以为主。则辄群然附和而谤诋其异己者。故虽其间不尽无操唐音者。而名不显于时。当是之时。吾少友周君曾锦晋琦。好读唐人诗。发为和平清远之作。而尤长于五言。往往入储光羲王维之门。余与之相会。或戏谓曰子之诗。其左于时矣乎。晋琦夷然而笑。既而武汉一鼓。清废而中国复其旧。夫国之将废也。其民愁苦。将兴也。其民和悦。然则彼之为愁苦之诗者。岂非兆清之废。而君之为平和之诗者。岂非兆中国之兴也耶。昔周之兴也。凤鸟鸣于岐山。请黄帝遗父老之闻读是诗者。其加额庆之曰此今日之凤声也。
浸远。弊又横生。愁苦忧叹。烦碎险怪之诗出焉。举天下之万象万事。一切皆以不平者而观之。以自煎灼。后生少年。苟得其一二巨子以为主。则辄群然附和而谤诋其异己者。故虽其间不尽无操唐音者。而名不显于时。当是之时。吾少友周君曾锦晋琦。好读唐人诗。发为和平清远之作。而尤长于五言。往往入储光羲王维之门。余与之相会。或戏谓曰子之诗。其左于时矣乎。晋琦夷然而笑。既而武汉一鼓。清废而中国复其旧。夫国之将废也。其民愁苦。将兴也。其民和悦。然则彼之为愁苦之诗者。岂非兆清之废。而君之为平和之诗者。岂非兆中国之兴也耶。昔周之兴也。凤鸟鸣于岐山。请黄帝遗父老之闻读是诗者。其加额庆之曰此今日之凤声也。明美堂集序(丁巳)
故韩光武二年戊戌。宁斋李公没。越七年国亡有兆。泽荣逃于淮南。又六年国亡之明年。公弟建升保卿走于鸭绿江北中国之地。至是保卿书于余曰。求礼黄季方,山清李明集。先后寄书劝余刊兄遗集。谓将与全湖全岭之士助之成。故吾方欲招手民开工。子吾兄之知己也。宁可不以一序明论吾兄之文哉。余执书太息曰。自古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然则委巷辁士。官府小吏之所记录。皆足为亡国之遗宝。况宁斋公。以吾韩诸王孙之名卿。而文章声望。与近世洪渊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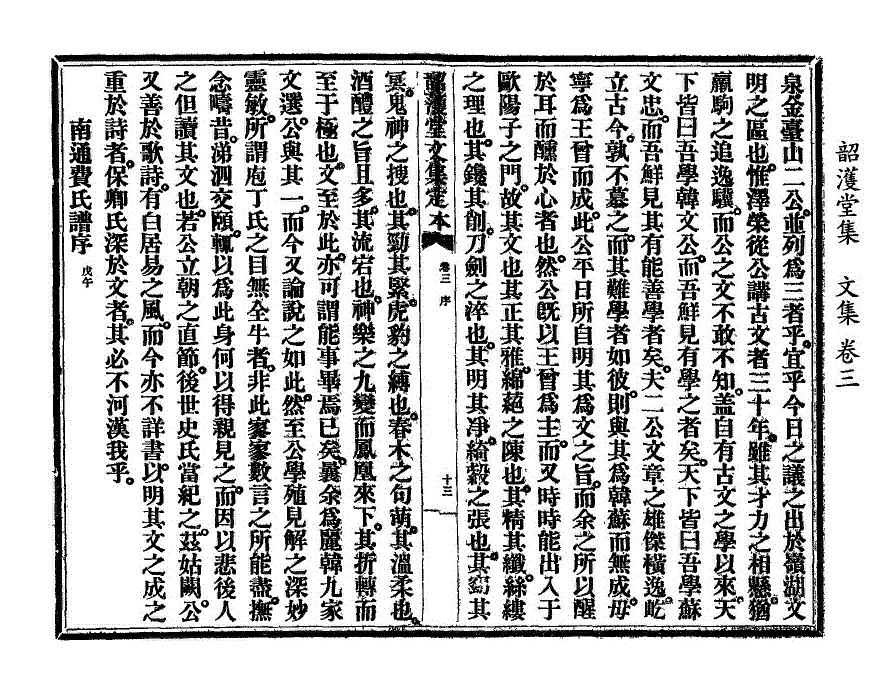 泉,金台山二公。并列为三者乎。宜乎今日之议之出于岭湖文明之区也。惟泽荣从公讲古文者三十年。虽其才力之相悬。犹羸驹之追逸骥。而公之文不敢不知。盖自有古文之学以来。天下皆曰吾学韩文公。而吾鲜见有学之者矣。天下皆曰吾学苏文忠。而吾鲜见其有能善学者矣。夫二公文章之雄杰横逸。屹立古今。孰不慕之。而其难学者如彼。则与其为韩苏而无成。毋宁为王曾而成。此公平日所自明其为文之旨。而余之所以醒于耳而醺于心者也。然公既以王曾为主。而又时时能出入于欧阳子之门。故其文也其正其雅。绵蕝之陈也。其精其纤。丝缕之理也。其镵其削。刀剑之淬也。其明其净。绮縠之张也。其窈其冥。鬼神之搜也。其劲其紧。虎豹之缚也。春木之句萌。其温柔也。酒醴之旨且多。其流宕也。神乐之九变而凤凰来下。其折转而至于极也。文至于此。亦可谓能事毕焉已矣。曩余为丽韩九家文选。公与其一。而今又论说之如此。然至公学殖见解之深妙灵敏。所谓庖丁氏之目无全牛者。非此寥寥数言之所能尽。抚念畴昔。涕泗交颐。辄以为此身何以得亲见之。而因以悲后人之但读其文也。若公立朝之直节。后世史氏当纪之。兹姑阙。公又善于歌诗。有白居易之风。而今亦不详书。以明其文之成之重于诗者。保卿氏深于文者。其必不河汉我乎。
泉,金台山二公。并列为三者乎。宜乎今日之议之出于岭湖文明之区也。惟泽荣从公讲古文者三十年。虽其才力之相悬。犹羸驹之追逸骥。而公之文不敢不知。盖自有古文之学以来。天下皆曰吾学韩文公。而吾鲜见有学之者矣。天下皆曰吾学苏文忠。而吾鲜见其有能善学者矣。夫二公文章之雄杰横逸。屹立古今。孰不慕之。而其难学者如彼。则与其为韩苏而无成。毋宁为王曾而成。此公平日所自明其为文之旨。而余之所以醒于耳而醺于心者也。然公既以王曾为主。而又时时能出入于欧阳子之门。故其文也其正其雅。绵蕝之陈也。其精其纤。丝缕之理也。其镵其削。刀剑之淬也。其明其净。绮縠之张也。其窈其冥。鬼神之搜也。其劲其紧。虎豹之缚也。春木之句萌。其温柔也。酒醴之旨且多。其流宕也。神乐之九变而凤凰来下。其折转而至于极也。文至于此。亦可谓能事毕焉已矣。曩余为丽韩九家文选。公与其一。而今又论说之如此。然至公学殖见解之深妙灵敏。所谓庖丁氏之目无全牛者。非此寥寥数言之所能尽。抚念畴昔。涕泗交颐。辄以为此身何以得亲见之。而因以悲后人之但读其文也。若公立朝之直节。后世史氏当纪之。兹姑阙。公又善于歌诗。有白居易之风。而今亦不详书。以明其文之成之重于诗者。保卿氏深于文者。其必不河汉我乎。南通费氏谱序(戊午)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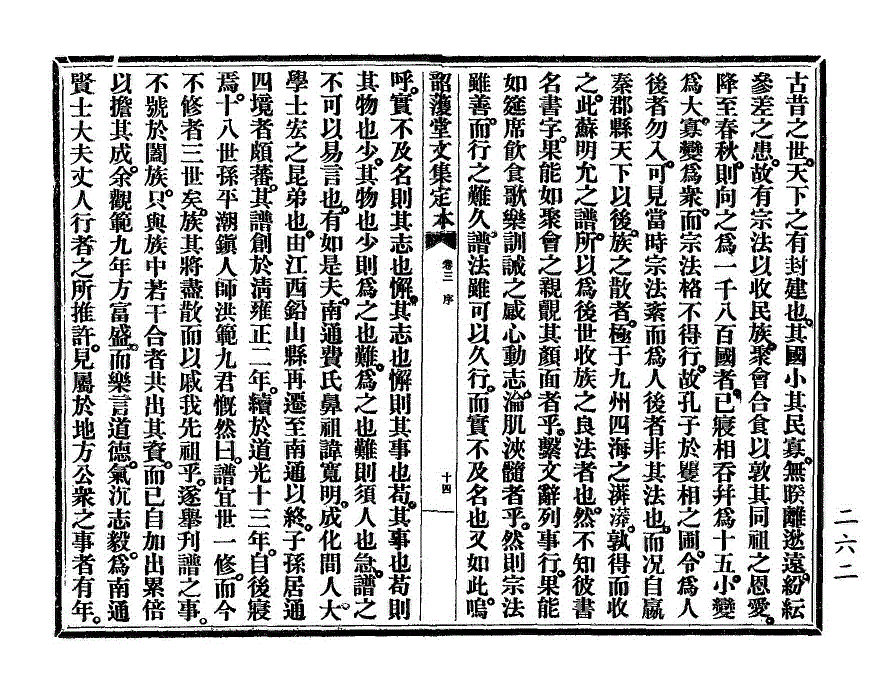 古昔之世。天下之有封建也。其国小其民寡。无睽离逖远。纷纭参差之患。故有宗法以收民族。聚会合食以敦其同祖之恩爱。降至春秋。则向之为一千八百国者。已寝相吞并为十五。小变为大。寡变为众。而宗法格不得行。故孔子于矍相之圃。令为人后者勿入。可见当时宗法紊而为人后者非其法也。而况自嬴秦郡县天下以后。族之散者。极于九州四海之漭漭。孰得而收之。此苏明允之谱。所以为后世收族之良法者也。然不知彼书名书字。果能如聚会之亲觌其颜面者乎。系文辞列事行。果能如筵席饮食歌乐训诫之感心动志。沦肌浃髓者乎。然则宗法虽善。而行之难久。谱法虽可以久行。而实不及名也又如此。呜呼。实不及名则其志也懈。其志也懈则其事也苟。其事也苟则其物也少。其物也少则为之也难。为之也难则须人也急。谱之不可以易言也。有如是夫。南通费氏鼻祖讳宽明。成化间人。大学士宏之昆弟也。由江西铅山县再迁至南通以终。子孙居通四境者颇蕃。其谱创于清雍正二年。续于道光十三年。自后寝焉。十八世孙平潮镇人师洪范九君慨然曰。谱宜世一修。而今不修者三世矣。族其将尽散而以戚我先祖乎。遂举刊谱之事。不号于阖族。只与族中若干合者共出其资。而己自加出累倍以担其成。余观范九年方富盛。而乐言道德。气沉志毅。为南通贤士大夫丈人行者之所推许。见属于地方公众之事者有年。
古昔之世。天下之有封建也。其国小其民寡。无睽离逖远。纷纭参差之患。故有宗法以收民族。聚会合食以敦其同祖之恩爱。降至春秋。则向之为一千八百国者。已寝相吞并为十五。小变为大。寡变为众。而宗法格不得行。故孔子于矍相之圃。令为人后者勿入。可见当时宗法紊而为人后者非其法也。而况自嬴秦郡县天下以后。族之散者。极于九州四海之漭漭。孰得而收之。此苏明允之谱。所以为后世收族之良法者也。然不知彼书名书字。果能如聚会之亲觌其颜面者乎。系文辞列事行。果能如筵席饮食歌乐训诫之感心动志。沦肌浃髓者乎。然则宗法虽善。而行之难久。谱法虽可以久行。而实不及名也又如此。呜呼。实不及名则其志也懈。其志也懈则其事也苟。其事也苟则其物也少。其物也少则为之也难。为之也难则须人也急。谱之不可以易言也。有如是夫。南通费氏鼻祖讳宽明。成化间人。大学士宏之昆弟也。由江西铅山县再迁至南通以终。子孙居通四境者颇蕃。其谱创于清雍正二年。续于道光十三年。自后寝焉。十八世孙平潮镇人师洪范九君慨然曰。谱宜世一修。而今不修者三世矣。族其将尽散而以戚我先祖乎。遂举刊谱之事。不号于阖族。只与族中若干合者共出其资。而己自加出累倍以担其成。余观范九年方富盛。而乐言道德。气沉志毅。为南通贤士大夫丈人行者之所推许。见属于地方公众之事者有年。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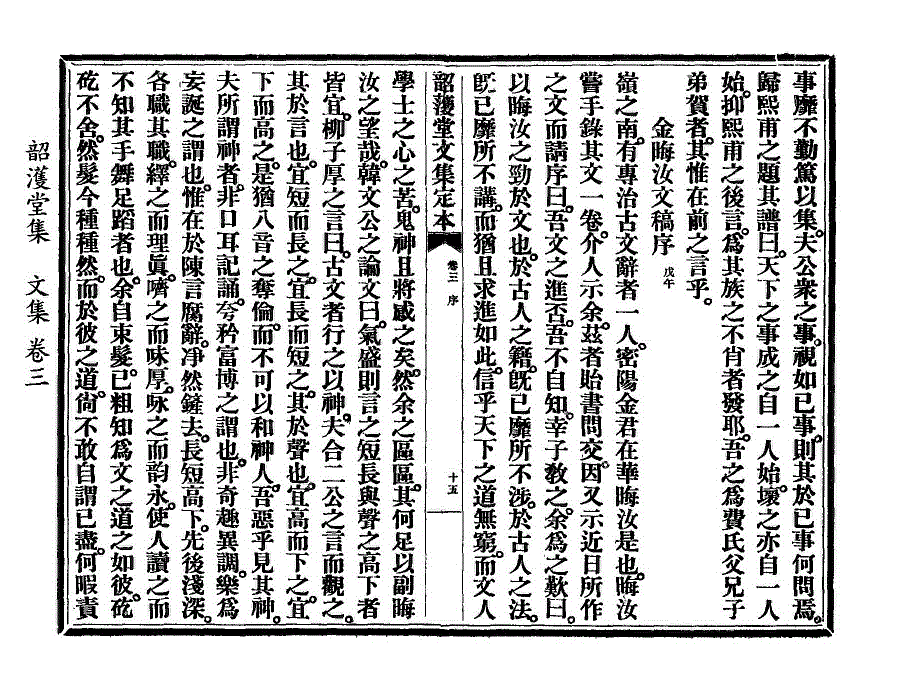 事靡不勤笃以集。夫公众之事。视如己事。则其于己事何问焉。归熙甫之题其谱曰。天下之事成之自一人始。坏之亦自一人始。抑熙甫之后言。为其族之不肖者发耶。吾之为费氏父兄子弟贺者。其惟在前之言乎。
事靡不勤笃以集。夫公众之事。视如己事。则其于己事何问焉。归熙甫之题其谱曰。天下之事成之自一人始。坏之亦自一人始。抑熙甫之后言。为其族之不肖者发耶。吾之为费氏父兄子弟贺者。其惟在前之言乎。金晦汝文稿序(戊午)
岭之南。有专治古文辞者一人。密阳金君在华晦汝是也。晦汝尝手录其文一卷。介人示余。兹者贻书问交。因又示近日所作之文而请序曰。吾文之进否。吾不自知。幸子教之。余为之叹曰。以晦汝之劲于文也。于古人之籍。既已靡所不涉。于古人之法。既已靡所不讲。而犹且求进如此。信乎天下之道无穷。而文人学士之心之苦。鬼神且将感之矣。然余之区区。其何足以副晦汝之望哉。韩文公之论文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子厚之言曰。古文者行之以神。夫合二公之言而观之。其于言也。宜短而长之。宜长而短之。其于声也。宜高而下之。宜下而高之。是犹八音之夺伦。而不可以和神人。吾恶乎见其神。夫所谓神者。非口耳记诵。夸矜富博之谓也。非奇趣异调。乐为妄诞之谓也。惟在于陈言腐辞。净然铲去。长短高下。先后浅深。各职其职。绎之而理真。哜之而味厚。咏之而韵永。使人读之而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余自束发。已粗知为文之道之如彼。矻矻不舍。然发今种种然。而于彼之道。尚不敢自谓已尽。何暇责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3L 页
 晦汝。惟晦汝努力自爱。进乎其所已进而精乎其所已精。无使向之二公专美于前。则余之获助也。且将多多矣。晦汝其许之也耶。
晦汝。惟晦汝努力自爱。进乎其所已进而精乎其所已精。无使向之二公专美于前。则余之获助也。且将多多矣。晦汝其许之也耶。茂亭诗稿序(戊午)
昔白居易为诗。有古诗人温柔敦厚之遗意。平易为体。广大为趣。精切为功。华丽为神。其辩不穷。滔滔如水。卓为中唐一代之钜工。后苏东坡病其平易。颇加嗤点。而师苏者奉为定论。又其后有人以苏之所病者为病。而直以天才断居易。与李白仙才李贺鬼才。并举为三。则是论也曷尝定哉。茂亭郑子自成童时。已能为诗。以李宁斋为师。以其弟丙朝宽卿为友。欢愉悲忧。一以是而陶之者四十年。而尤有敏才。其在海岛时。尝一日成百绝句。何其奇矣。茂亭子近次其诗。为若干卷。以不佞为生平文字之契合者。走书徵言。嗟夫。不佞之齿。今已颓矣。其何足复与于风雅之事而为之说乎。惟以茂亭之诗。于居易为近。故略论居易。俾读是诗者。比类以观之。
愚坞金翁六十八岁寿序(己未)
清道少年金君镛源走书言曰。子吾师曹深斋先生之所好也。愿藉是得子文。以寿我鳏穷大父。因略道大父之才德及生平阅历。曰大父名基孝。号愚坞。以故韩 哲宗壬子生。生有玉貌。心亦如之。简于言而敏于事。处清约而不事货利。少工举业。屡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4H 页
 举于乡。多居首列。然不肯媚附于有力者。故终于无成。晚以驾洛王苗裔。除崇善殿参奉。后进议官衔。至通政大夫之爵。夫人之寿命禀于天。然所以能寿者。不独恃天而已。逢时值会。得意行志。有车马冠剑之光耀者。所以鬯寿之气也。富饶丰盈。无求不得。有甘食美服之快乐者。所以厚寿之基也。令妻贤配。白首偕老。所以安其寿也。国家清明。朝野欢康。所以娱其寿也。今镛源君之所愿于大父者。百岁之寿不足为多。然君之大父怀才抱德而名位不副。谁与鬯之。仅衣仅食以支岁时。谁与厚之。入其室而阒无良匹矣。谁与安之。所遇于国家者。天翻地覆而日月晦蚀矣。谁与娱之。此君之所以汲汲于颂祝。而欲援余以为助者也。余虽衰老。言辞呐涩。而其可以终于闭默而已乎。盖人之子孙。自其人观之。固属于其身之外。然其实则一气之相与贯通。犹木之根枝。枝苟旺则根宁有独不旺者乎。洪范五福。不言子孙者。以子孙有贤不肖之异。苟其不幸而不肖。则足以丧其家故也。然使子孙诚贤而不不肖。则父与祖之所乐者。孰有加于此哉。闻之深斋。曰吾之学徒。有成生纯永,金生镛源二人最秀出。其进莫量。繇此言之。君之大父。虽于向所言四者无其一。而子孙之乐。有君在焉。是乐也非寿之道乎。吾请举此而祝子之大父。子其勿退然深避。而且益懋于学。以实深斋之言也哉。
举于乡。多居首列。然不肯媚附于有力者。故终于无成。晚以驾洛王苗裔。除崇善殿参奉。后进议官衔。至通政大夫之爵。夫人之寿命禀于天。然所以能寿者。不独恃天而已。逢时值会。得意行志。有车马冠剑之光耀者。所以鬯寿之气也。富饶丰盈。无求不得。有甘食美服之快乐者。所以厚寿之基也。令妻贤配。白首偕老。所以安其寿也。国家清明。朝野欢康。所以娱其寿也。今镛源君之所愿于大父者。百岁之寿不足为多。然君之大父怀才抱德而名位不副。谁与鬯之。仅衣仅食以支岁时。谁与厚之。入其室而阒无良匹矣。谁与安之。所遇于国家者。天翻地覆而日月晦蚀矣。谁与娱之。此君之所以汲汲于颂祝。而欲援余以为助者也。余虽衰老。言辞呐涩。而其可以终于闭默而已乎。盖人之子孙。自其人观之。固属于其身之外。然其实则一气之相与贯通。犹木之根枝。枝苟旺则根宁有独不旺者乎。洪范五福。不言子孙者。以子孙有贤不肖之异。苟其不幸而不肖。则足以丧其家故也。然使子孙诚贤而不不肖。则父与祖之所乐者。孰有加于此哉。闻之深斋。曰吾之学徒。有成生纯永,金生镛源二人最秀出。其进莫量。繇此言之。君之大父。虽于向所言四者无其一。而子孙之乐。有君在焉。是乐也非寿之道乎。吾请举此而祝子之大父。子其勿退然深避。而且益懋于学。以实深斋之言也哉。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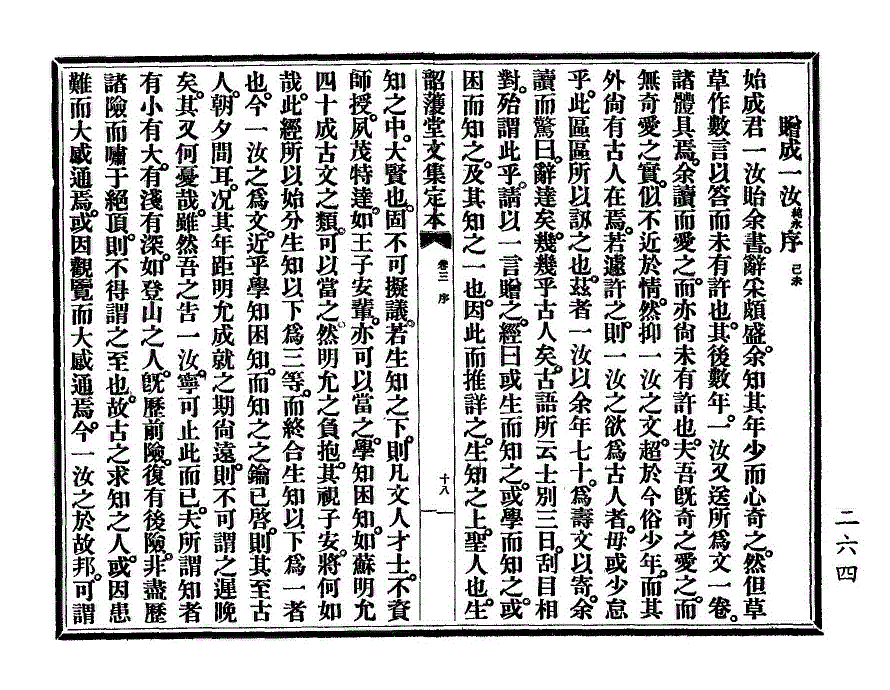 赠成一汝(纯永)序(己未)
赠成一汝(纯永)序(己未)始成君一汝贻余书。辞采颇盛。余知其年少而心奇之。然但草草作数言以答而未有许也。其后数年。一汝又送所为文一卷。诸体具焉。余读而爱之。而亦尚未有许也。夫吾既奇之爱之。而无奇爱之实。似不近于情。然抑一汝之文。超于今俗少年。而其外尚有古人在焉。若遽许之。则一汝之欲为古人者。毋或少怠乎。此区区所以讱之也。兹者一汝以余年七十。为寿文以寄。余读而惊曰。辞达矣。几几乎古人矣。古语所云士别三日。刮目相对。殆谓此乎。请以一言赠之。经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因此而推详之。生知之上。圣人也。生知之中。大贤也。固不可拟议。若生知之下。则凡文人才士。不资师授。夙茂特达。如王子安辈。亦可以当之。学知困知。如苏明允四十成古文之类。可以当之。然明允之负抱。其视子安。将何如哉。此经所以始分生知以下为三等。而终合生知以下为一者也。今一汝之为文。近乎学知困知。而知之之钥已启。则其至古人。朝夕间耳。况其年距明允成就之期尚远。则不可谓之迟晚矣。其又何忧哉。虽然吾之告一汝。宁可止此而已。夫所谓知者有小有大。有浅有深。如登山之人。既历前险。复有后险。非尽历诸险而啸于绝顶。则不得谓之至也。故古之求知之人。或因患难而大感通焉。或因观览而大感通焉。今一汝之于故邦。可谓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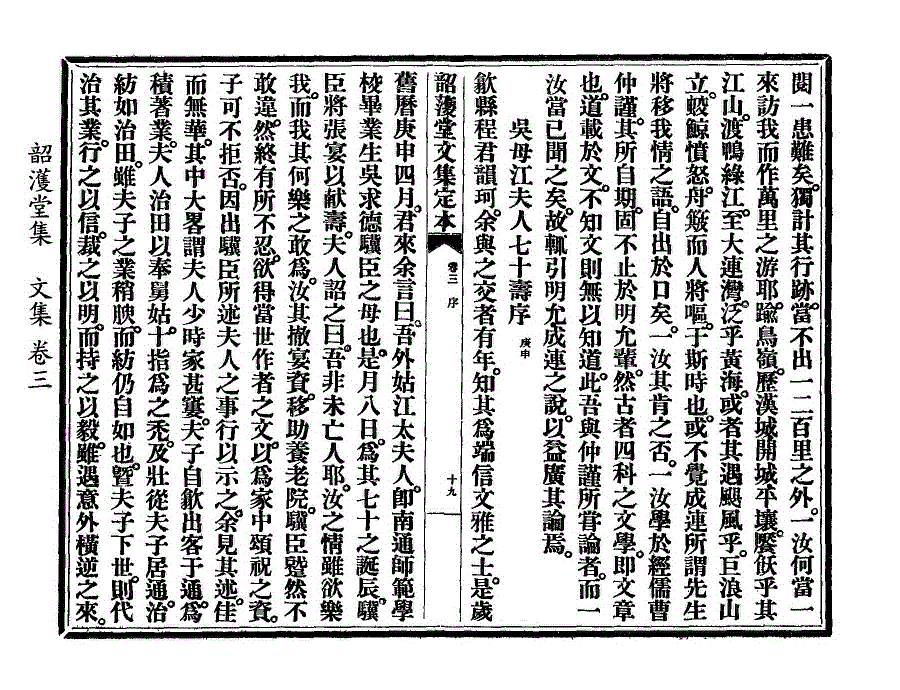 阅一患难矣。独计其行迹。当不出一二百里之外。一汝何当一来访我而作万里之游耶。踰鸟岭。历汉城,开城,平壤。餍饫乎其江山。渡鸭绿江。至大连湾。泛乎黄海。或者其遇飓风乎。巨浪山立。蛟鲸愤怒。舟簸而人将呕。于斯时也。或不觉成连所谓先生将移我情之语。自出于口矣。一汝其肯之否。一汝学于经儒曹仲谨。其所自期。固不止于明允辈。然古者四科之文学。即文章也。道载于文。不知文则无以知道。此吾与仲谨所尝论者。而一汝当已闻之矣。故辄引明允,成连之说。以益广其论焉。
阅一患难矣。独计其行迹。当不出一二百里之外。一汝何当一来访我而作万里之游耶。踰鸟岭。历汉城,开城,平壤。餍饫乎其江山。渡鸭绿江。至大连湾。泛乎黄海。或者其遇飓风乎。巨浪山立。蛟鲸愤怒。舟簸而人将呕。于斯时也。或不觉成连所谓先生将移我情之语。自出于口矣。一汝其肯之否。一汝学于经儒曹仲谨。其所自期。固不止于明允辈。然古者四科之文学。即文章也。道载于文。不知文则无以知道。此吾与仲谨所尝论者。而一汝当已闻之矣。故辄引明允,成连之说。以益广其论焉。吴母江夫人七十寿序(庚申)
歙县程君韵珂。余与之交者有年。知其为端信文雅之士。是岁旧历庚申四月。君来余言曰。吾外姑江太夫人。即南通师范学校毕业生吴求德骥臣之母也。是月八日。为其七十之诞辰。骥臣将张宴以献寿。夫人诏之曰。吾非未亡人耶。汝之情虽欲乐我。而我其何乐之敢为。汝其撤宴资。移助养老院。骥臣蹴然不敢违。然终有所不忍。欲得当世作者之文。以为家中颂祝之资。子可不拒否。因出骥臣所述夫人之事行以示之。余见其述。佳而无华。其中大略谓夫人少时家甚窭。夫子自歙出客于通。为积著业。夫人治田以奉舅姑。十指为之秃。及壮从夫子居通。治纺如治田。虽夫子之业稍腴。而纺仍自如也。暨夫子下世。则代治其业。行之以信。裁之以明。而持之以毅。虽遇意外横逆之来。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5L 页
 而不动声色以弭之。如是者几年。业遂益腴而至于大矣。尤能轻财。通歙之间。所阴佽公益善举及贫族婚丧之事者。不可胜数。而至其自奉则布素补缀之为甘。此皆其可寿之实也。呜呼。夫人之为命。与男子不同。贤淑之行。率多掩翳于闺壸之内。有心君子固欲扼腕而列阐之。而况乎夫人才德之出类拔群者乎。又况于程君之言之可信。与其子之述之无华者乎。余故不辞而为之一言。系之以歌曰。夫何此一人兮。秀出闺閤。其仁其智兮。丈夫不若。猗其贤兮。贤而有禄。彼云之君兮。徕护其室。猗其禄兮。禄而且寿。寿而加寿兮。如彼狼岫。
而不动声色以弭之。如是者几年。业遂益腴而至于大矣。尤能轻财。通歙之间。所阴佽公益善举及贫族婚丧之事者。不可胜数。而至其自奉则布素补缀之为甘。此皆其可寿之实也。呜呼。夫人之为命。与男子不同。贤淑之行。率多掩翳于闺壸之内。有心君子固欲扼腕而列阐之。而况乎夫人才德之出类拔群者乎。又况于程君之言之可信。与其子之述之无华者乎。余故不辞而为之一言。系之以歌曰。夫何此一人兮。秀出闺閤。其仁其智兮。丈夫不若。猗其贤兮。贤而有禄。彼云之君兮。徕护其室。猗其禄兮。禄而且寿。寿而加寿兮。如彼狼岫。重编韩代崧阳耆旧传序(庚申)
往在故韩 光武帝甲申。余年三十五。自开城城中。移居其北古德里之峡。地僻人稀。乃取地志。作崧阳耆旧传。一年而毕。至戊子始序之。丙申。三从弟丰基郡守士圭。自任所送金于汉京宦寓。使刊其书。实罕事也。然所刊百馀本。立散尽于搢绅间。而鲜出京外。故迨拙集之刊。附入以再刊矣。今而思之。是书自是一家之文。不可以寄附埋没于闲漫述作之中也。且于昏晓枕席之上。就而追绎。则义例之疏。字句之疵。亦颇有焉。谓我已耄。置之姑息。岂卫武抑戒之意哉。遂乃拔出其编。磨之涤之。因付于印。为可以稍得广布焉。抑有一感。是书之名。与旧不同。时之变使之为也。噫夫为此时者谁欤。其天欤其人欤。其枯槁寂寞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三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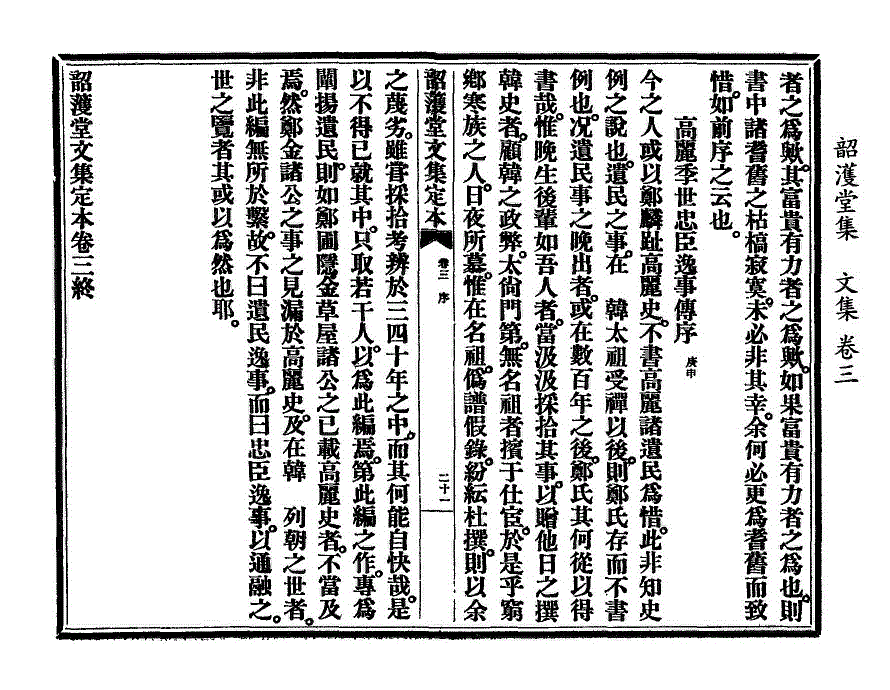 者之为欤。其富贵有力者之为欤。如果富贵有力者之为也。则书中诸耆旧之枯槁寂寞。未必非其幸。余何必更为耆旧而致惜。如前序之云也。
者之为欤。其富贵有力者之为欤。如果富贵有力者之为也。则书中诸耆旧之枯槁寂寞。未必非其幸。余何必更为耆旧而致惜。如前序之云也。高丽季世忠臣逸事传序(庚申)
今之人或以郑麟趾高丽史。不书高丽诸遗民为惜。此非知史例之说也。遗民之事。在 韩太祖受禅以后。则郑氏存而不书例也。况遗民事之晚出者。或在数百年之后。郑氏其何从以得书哉。惟晚生后辈如吾人者。当汲汲采拾其事。以赠他日之撰韩史者。顾韩之政弊。太尚门第。无名祖者摈于仕宦。于是乎穷乡寒族之人。日夜所慕。惟在名祖。伪谱假录。纷纭杜撰。则以余之蔑劣。虽尝采拾考辨于三四十年之中。而其何能自快哉。是以不得已就其中。只取若干人。以为此编焉。第此编之作。专为阐扬遗民。则如郑圃隐,金草屋诸公之已载高丽史者。不当及焉。然郑金诸公之事之见漏于高丽史。及在韩 列朝之世者。非此编无所于系。故不曰遗民逸事。而曰忠臣逸事。以通融之。世之览者其或以为然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