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x 页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序
序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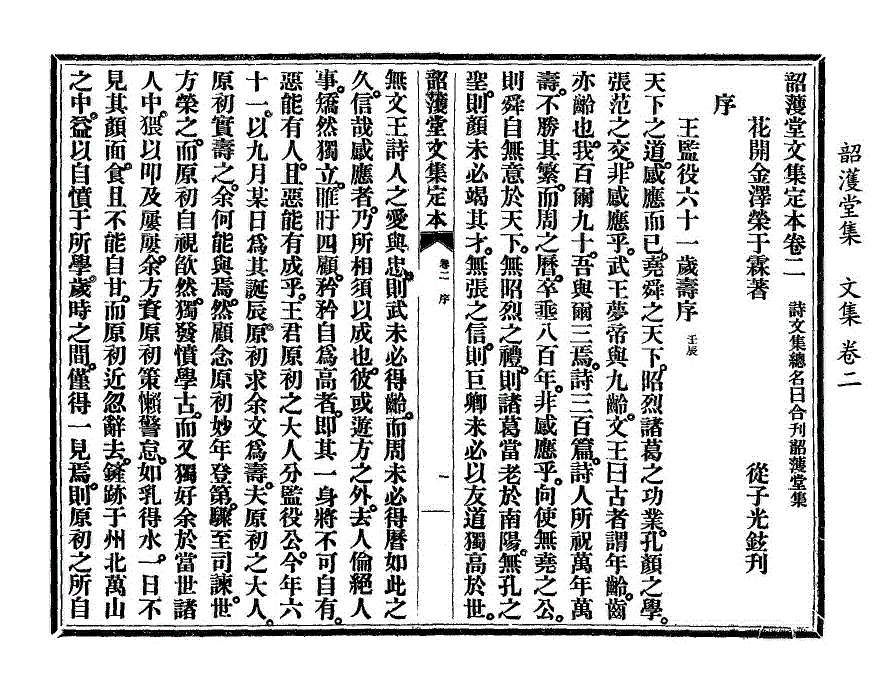 王监役六十一岁寿序(壬辰)
王监役六十一岁寿序(壬辰)天下之道。感应而已。尧舜之天下。昭烈诸葛之功业。孔颜之学。张范之交。非感应乎。武王梦帝与九龄。文王曰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诗三百篇。诗人所祝万年万寿。不胜其繁。而周之历。卒垂八百年。非感应乎。向使无尧之公。则舜自无意于天下。无昭烈之礼。则诸葛当老于南阳。无孔之圣。则颜未必竭其才。无张之信。则巨卿未必以友道独高于世。无文王诗人之爱与忠。则武未必得龄。而周未必得历如此之久。信哉感应者。乃所相须以成也。彼或游方之外。去人伦绝人事。矫然独立。睢盱四顾。矜矜自为高者。即其一身将不可自有。恶能有人。且恶能有成乎。王君原初之大人分监役公。今年六十一。以九月某日为其诞辰。原初求余文为寿。夫原初之大人。原初实寿之。余何能与焉。然顾念原初妙年登第。骤至司谏。世方荣之。而原初自视欿然。独发愤学古。而又独好余于当世诸人中。猥以叩及屡屡。余方资原初策懒警怠。如乳得水。一日不见其颜面。食且不能自甘。而原初近忽辞去。铲迹于州北万山之中。益以自愤于所学。岁时之间。仅得一见焉。则原初之所自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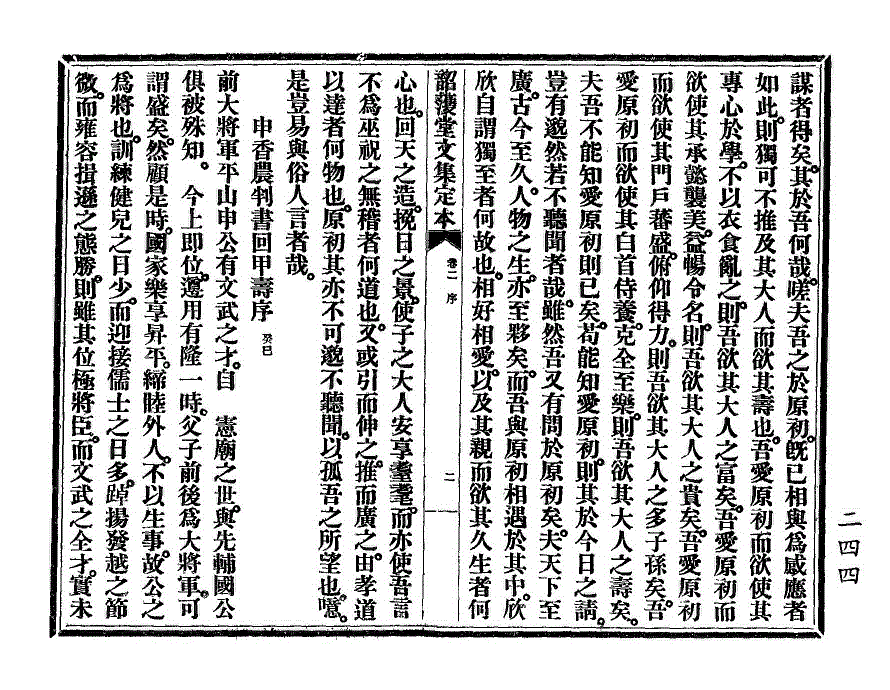 谋者得矣。其于吾何哉。嗟夫吾之于原初。既已相与为感应者如此。则独可不推及其大人而欲其寿也。吾爱原初而欲使其专心于学。不以衣食乱之。则吾欲其大人之富矣。吾爱原初而欲使其承懿袭美。益畅令名。则吾欲其大人之贵矣。吾爱原初而欲使其门户蕃盛。俯仰得力。则吾欲其大人之多子孙矣。吾爱原初而欲使其白首侍养。克全至乐。则吾欲其大人之寿矣。夫吾不能知爱原初则已矣。苟能知爱原初。则其于今日之请。岂有邈然若不听闻者哉。虽然吾又有问于原初矣。夫天下至广。古今至久。人物之生。亦至夥矣。而吾与原初相遇于其中。欣欣自谓独至者何故也。相好相爱。以及其亲而欲其久生者何心也。回天之造。挽日之景。使子之大人安享耋耄。而亦使吾言不为巫祝之无稽者何道也。又或引而伸之。推而广之。由孝道以达者何物也。原初其亦不可邈不听闻。以孤吾之所望也。噫。是岂易与俗人言者哉。
谋者得矣。其于吾何哉。嗟夫吾之于原初。既已相与为感应者如此。则独可不推及其大人而欲其寿也。吾爱原初而欲使其专心于学。不以衣食乱之。则吾欲其大人之富矣。吾爱原初而欲使其承懿袭美。益畅令名。则吾欲其大人之贵矣。吾爱原初而欲使其门户蕃盛。俯仰得力。则吾欲其大人之多子孙矣。吾爱原初而欲使其白首侍养。克全至乐。则吾欲其大人之寿矣。夫吾不能知爱原初则已矣。苟能知爱原初。则其于今日之请。岂有邈然若不听闻者哉。虽然吾又有问于原初矣。夫天下至广。古今至久。人物之生。亦至夥矣。而吾与原初相遇于其中。欣欣自谓独至者何故也。相好相爱。以及其亲而欲其久生者何心也。回天之造。挽日之景。使子之大人安享耋耄。而亦使吾言不为巫祝之无稽者何道也。又或引而伸之。推而广之。由孝道以达者何物也。原初其亦不可邈不听闻。以孤吾之所望也。噫。是岂易与俗人言者哉。申香农判书回甲寿序(癸巳)
前大将军平山申公有文武之才。自 宪庙之世。与先辅国公俱被殊知。 今上即位。遵用有隆一时。父子前后为大将军。可谓盛矣。然顾是时。国家乐享升平。缔睦外人。不以生事。故公之为将也。训练健儿之日少。而迎接儒士之日多。踔扬发越之节微。而雍容揖逊之态胜。则虽其位极将臣。而文武之全才。实未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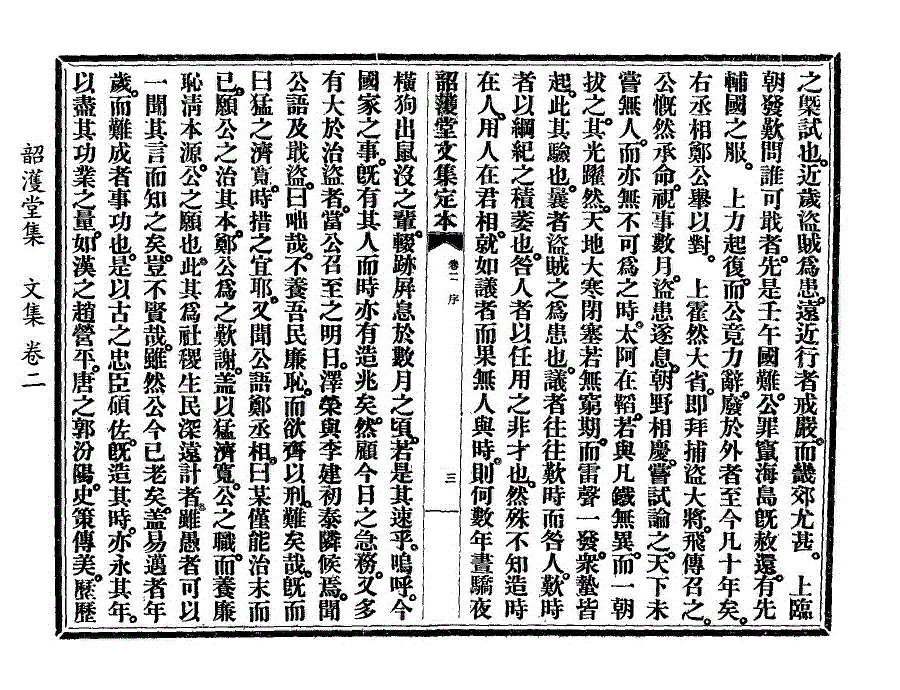 之槩试也。近岁盗贼为患。远近行者戒严。而畿郊尤甚。 上临朝发叹问谁可戢者。先是壬午国难。公罪窜海岛既赦还。有先辅国之服。 上力起复。而公竟力辞。废于外者至今凡十年矣。右丞相郑公举以对。 上霍然大省。即拜捕盗大将。飞传召之。公慨然承命。视事数月。盗患遂息。朝野相庆。尝试论之。天下未尝无人。而亦无不可为之时。太阿在韬。若与凡铁无异。而一朝拔之。其光跃然。天地大寒闭塞若无穷期。而雷声一发。众蛰皆起。此其验也。曩者盗贼之为患也。议者往往叹时而咎人。叹时者以纲纪之积萎也。咎人者以任用之非才也。然殊不知造时在人。用人在君相。就如议者而果无人与时。则何数年昼骄夜横狗出鼠没之辈。辍迹屏息于数月之顷。若是其速乎。呜呼。今国家之事。既有其人而时亦有造兆矣。然顾今日之急务。又多有大于治盗者。当公召至之明日。泽荣与李建初泰邻候焉。闻公语及戢盗。曰咄哉。不养吾民廉耻。而欲齐以刑。难矣哉。既而曰猛之济宽。时措之宜耶。又闻公语郑丞相。曰某仅能治末而已。愿公之治其本。郑公为之叹谢。盖以猛济宽。公之职。而养廉耻清本源。公之愿也。此其为社稷生民深远计者。虽愚者可以一闻其言而知之矣。岂不贤哉。虽然公今已老矣。盖易迈者年岁。而难成者事功也。是以古之忠臣硕佐。既造其时。亦永其年。以尽其功业之量。如汉之赵营平。唐之郭汾阳。史策传美。历历
之槩试也。近岁盗贼为患。远近行者戒严。而畿郊尤甚。 上临朝发叹问谁可戢者。先是壬午国难。公罪窜海岛既赦还。有先辅国之服。 上力起复。而公竟力辞。废于外者至今凡十年矣。右丞相郑公举以对。 上霍然大省。即拜捕盗大将。飞传召之。公慨然承命。视事数月。盗患遂息。朝野相庆。尝试论之。天下未尝无人。而亦无不可为之时。太阿在韬。若与凡铁无异。而一朝拔之。其光跃然。天地大寒闭塞若无穷期。而雷声一发。众蛰皆起。此其验也。曩者盗贼之为患也。议者往往叹时而咎人。叹时者以纲纪之积萎也。咎人者以任用之非才也。然殊不知造时在人。用人在君相。就如议者而果无人与时。则何数年昼骄夜横狗出鼠没之辈。辍迹屏息于数月之顷。若是其速乎。呜呼。今国家之事。既有其人而时亦有造兆矣。然顾今日之急务。又多有大于治盗者。当公召至之明日。泽荣与李建初泰邻候焉。闻公语及戢盗。曰咄哉。不养吾民廉耻。而欲齐以刑。难矣哉。既而曰猛之济宽。时措之宜耶。又闻公语郑丞相。曰某仅能治末而已。愿公之治其本。郑公为之叹谢。盖以猛济宽。公之职。而养廉耻清本源。公之愿也。此其为社稷生民深远计者。虽愚者可以一闻其言而知之矣。岂不贤哉。虽然公今已老矣。盖易迈者年岁。而难成者事功也。是以古之忠臣硕佐。既造其时。亦永其年。以尽其功业之量。如汉之赵营平。唐之郭汾阳。史策传美。历历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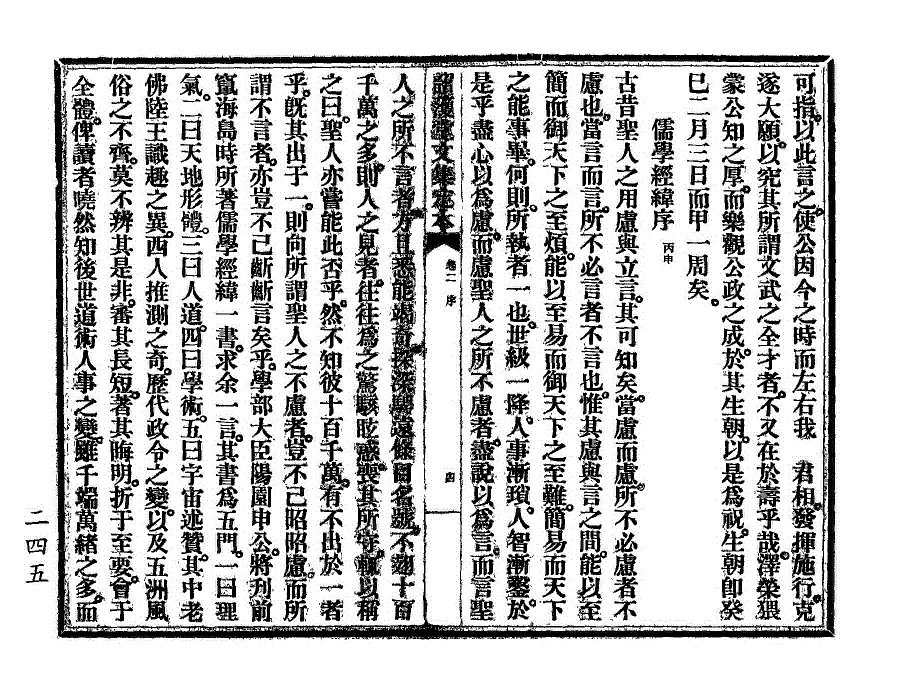 可指。以此言之。使公因今之时而左右我 君相。发挥施行。克遂大愿。以究其所谓文武之全才者。不又在于寿乎哉。泽荣猥蒙公知之厚。而乐观公政之成。于其生朝。以是为祝。生朝即癸巳二月三日而甲一周矣。
可指。以此言之。使公因今之时而左右我 君相。发挥施行。克遂大愿。以究其所谓文武之全才者。不又在于寿乎哉。泽荣猥蒙公知之厚。而乐观公政之成。于其生朝。以是为祝。生朝即癸巳二月三日而甲一周矣。儒学经纬序(丙申)
古昔圣人之用虑与立言。其可知矣。当虑而虑。所不必虑者不虑也。当言而言。所不必言者不言也。惟其虑与言之间。能以至简而御天下之至烦。能以至易而御天下之至难。简易而天下之能事毕。何则。所执者一也。世级一降。人事渐琐。人智渐凿。于是乎尽心以为虑。而虑圣人之所不虑者。尽说以为言。而言圣人之所不言者。方且悉能竭奇。探深骋远条目名号。不翅十百千万之多。则人之见者。往往为之惊骇眩惑。丧其所守。辄以称之曰。圣人亦尝能此否乎。然不知彼十百千万。有不出于一者乎。既其出于一。则向所谓圣人之不虑者。岂不已昭昭虑。而所谓不言者。亦岂不已龂龂言矣乎。学部大臣阳园申公。将刊前窜海岛时所著儒学经纬一书。求余一言。其书为五门。一曰理气。二曰天地形体。三曰人道。四曰学术。五曰宇宙述赞。其中老佛陆王识趣之异。西人推测之奇。历代政令之变。以及五洲风俗之不齐。莫不辨其是非。审其长短。著其晦明。折于至要。会于全体。俾读者晓然知后世道术人事之变。虽千端万绪之多。而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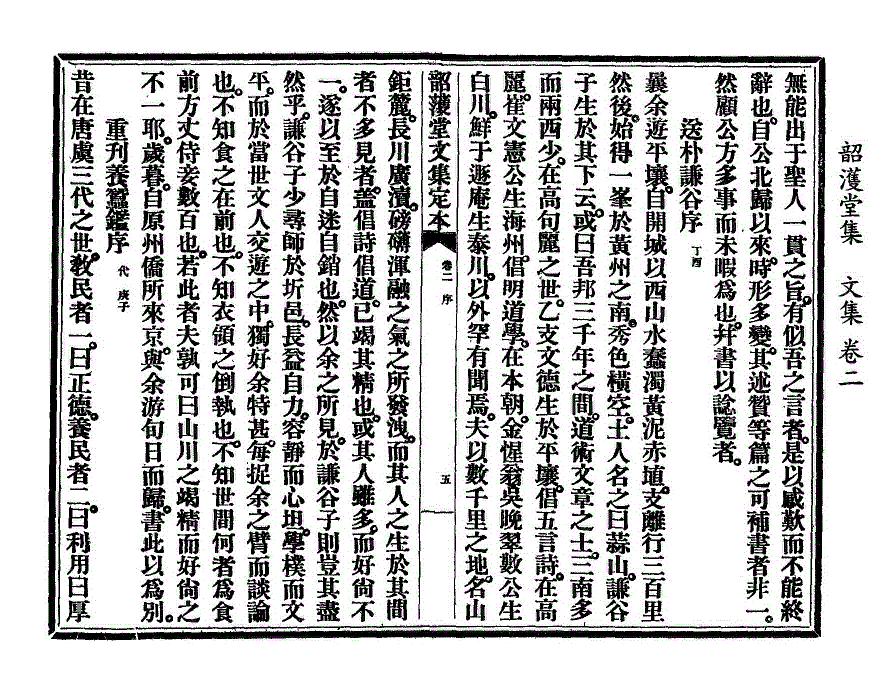 无能出于圣人一贯之旨。有似吾之言者。是以感叹而不能终辞也。自公北归以来。时形多变。其述赞等篇之可补书者非一。然顾公方多事而未暇为也。并书以谂览者。
无能出于圣人一贯之旨。有似吾之言者。是以感叹而不能终辞也。自公北归以来。时形多变。其述赞等篇之可补书者非一。然顾公方多事而未暇为也。并书以谂览者。送朴谦谷序(丁酉)
曩余游平壤。自开城以西山水蠢浊黄泥赤埴。支离行三百里然后。始得一峰于黄州之南。秀色横空。土人名之曰蒜山。谦谷子生于其下云。或曰吾邦三千年之间。道术文章之士。三南多而两西少。在高句丽之世。乙支文德生于平壤。倡五言诗。在高丽。崔文宪公生海州。倡明道学。在本朝。金惺翁,吴晚翠数公生白川。鲜于遁庵生泰川。以外罕有闻焉。夫以数千里之地。名山钜麓。长川广渎。磅礴浑融之气之所发泄。而其人之生于其间者不多见者。盖倡诗倡道。已竭其精也。或其人虽多。而好尚不一。遂以至于自迷自销也。然以余之所见。于谦谷子则岂其尽然乎。谦谷子少寻师于圻邑。长益自力。容静而心坦。学朴而文平。而于当世文人交游之中。独好余特甚。每捉余之臂而谈论也。不知食之在前也。不知衣领之倒执也。不知世间何者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也。若此者夫孰可曰山川之竭精而好尚之不一耶。岁暮。自原州侨所来京。与余游旬日而归。书此以为别。
重刊养蚕鉴序(代○庚子)
昔在唐虞三代之世。教民者一。曰正德。养民者二。曰利用曰厚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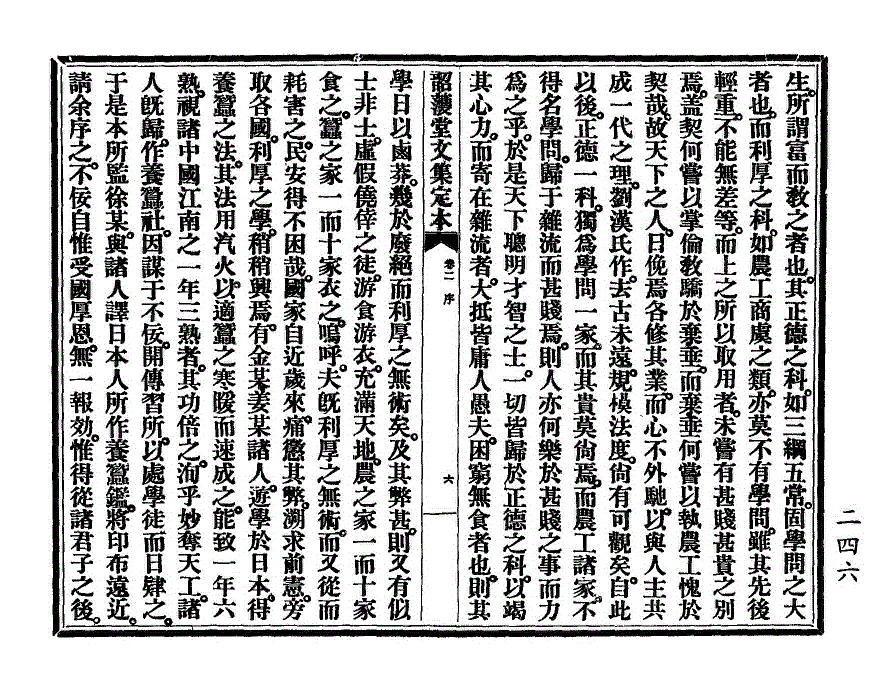 生。所谓富而教之者也。其正德之科。如三纲五常。固学问之大者也。而利厚之科。如农工商虞之类。亦莫不有学问。虽其先后轻重。不能无差等。而上之所以取用者。未尝有甚贱甚贵之别焉。盖契何尝以掌伦教骄于弃,垂。而弃,垂何尝以执农工愧于契哉。故天下之人。日俛焉各修其业。而心不外驰。以与人主共成一代之理。刘汉氏作。去古未远。规模法度。尚有可观矣。自此以后。正德一科。独为学问一家。而其贵莫尚焉。而农工诸家。不得名学问。归于杂流而甚贱焉。则人亦何乐于甚贱之事而力为之乎。于是天下聪明才智之士。一切皆归于正德之科。以竭其心力。而寄在杂流者。大抵皆庸人愚夫。困穷无食者也。则其学日以卤莽。几于废绝而利厚之无术矣。及其弊甚。则又有似士非士。虚假侥倖之徒。游食游衣。充满天地。农之家一而十家食之。蚕之家一而十家衣之。呜呼。夫既利厚之无术。而又从而耗害之。民安得不困哉。国家自近岁来。痛惩其弊。溯求前宪。旁取各国。利厚之学。稍稍兴焉。有金某,姜某诸人。游学于日本。得养蚕之法。其法用汽火。以适蚕之寒暖而速成之。能致一年六熟。视诸中国江南之一年三熟者。其功倍之。洵乎妙夺天工。诸人既归。作养蚕社。因谋于不佞。开传习所。以处学徒而日肄之。于是本所监徐某。与诸人译日本人所作养蚕鉴。将印布远近。请余序之。不佞自惟受国厚恩。无一报效。惟得从诸君子之后。
生。所谓富而教之者也。其正德之科。如三纲五常。固学问之大者也。而利厚之科。如农工商虞之类。亦莫不有学问。虽其先后轻重。不能无差等。而上之所以取用者。未尝有甚贱甚贵之别焉。盖契何尝以掌伦教骄于弃,垂。而弃,垂何尝以执农工愧于契哉。故天下之人。日俛焉各修其业。而心不外驰。以与人主共成一代之理。刘汉氏作。去古未远。规模法度。尚有可观矣。自此以后。正德一科。独为学问一家。而其贵莫尚焉。而农工诸家。不得名学问。归于杂流而甚贱焉。则人亦何乐于甚贱之事而力为之乎。于是天下聪明才智之士。一切皆归于正德之科。以竭其心力。而寄在杂流者。大抵皆庸人愚夫。困穷无食者也。则其学日以卤莽。几于废绝而利厚之无术矣。及其弊甚。则又有似士非士。虚假侥倖之徒。游食游衣。充满天地。农之家一而十家食之。蚕之家一而十家衣之。呜呼。夫既利厚之无术。而又从而耗害之。民安得不困哉。国家自近岁来。痛惩其弊。溯求前宪。旁取各国。利厚之学。稍稍兴焉。有金某,姜某诸人。游学于日本。得养蚕之法。其法用汽火。以适蚕之寒暖而速成之。能致一年六熟。视诸中国江南之一年三熟者。其功倍之。洵乎妙夺天工。诸人既归。作养蚕社。因谋于不佞。开传习所。以处学徒而日肄之。于是本所监徐某。与诸人译日本人所作养蚕鉴。将印布远近。请余序之。不佞自惟受国厚恩。无一报效。惟得从诸君子之后。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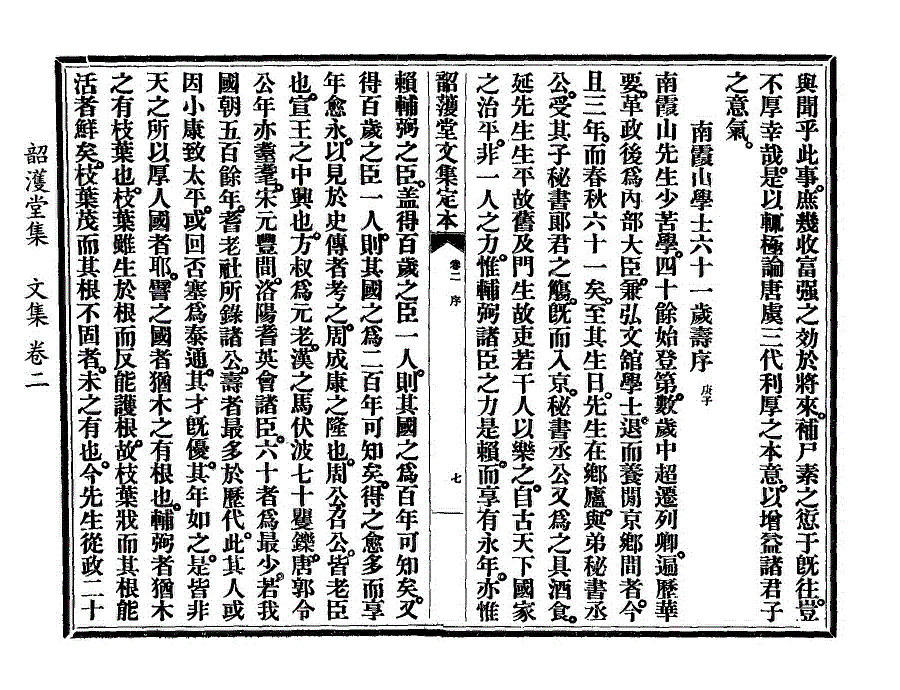 与闻乎此事。庶几收富强之效于将来。补尸素之愆于既往。岂不厚幸哉。是以辄极论唐虞三代利厚之本意。以增益诸君子之意气。
与闻乎此事。庶几收富强之效于将来。补尸素之愆于既往。岂不厚幸哉。是以辄极论唐虞三代利厚之本意。以增益诸君子之意气。南霞山学士六十一岁寿序(庚子)
南霞山先生少苦学。四十馀始登第。数岁中超迁列卿。遍历华要。革政后为内部大臣。兼弘文馆学士。退而养閒京乡间者。今且三年。而春秋六十一矣。至其生日。先生在乡庐。与弟秘书丞公。受其子秘书郎君之觞。既而入京。秘书丞公又为之具酒食。延先生生平故旧及门生故吏若干人以乐之。自古天下国家之治平。非一人之力。惟辅弼诸臣之力是赖。而享有永年。亦惟赖辅弼之臣。盖得百岁之臣一人。则其国之为百年可知矣。又得百岁之臣一人。则其国之为二百年可知矣。得之愈多而享年愈永。以见于史传者考之。周成康之隆也。周公,召公。皆老臣也。宣王之中兴也。方叔为元老。汉之马伏波七十矍铄。唐郭令公年亦耋耄。宋元丰间。洛阳耆英会诸臣。六十者为最少。若我国朝五百馀年。耆老社所录诸公。寿者最多于历代。此其人或因小康致太平。或回否塞为泰通。其才既优。其年如之。是皆非天之所以厚人国者耶。譬之国者犹木之有根也。辅弼者犹木之有枝叶也。枝叶虽生于根而反能护根。故枝叶戕而其根能活者鲜矣。枝叶茂而其根不固者。未之有也。今先生从政二十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7L 页
 年之间。所经历国家安危否泰。所以焦心肝劳筋骸者不一。而发之种种。已如此矣。然而天下之事尚无穷。先生之年尚未耄。而 天子行且复用先生矣。然则泽荣当何以为先生寿。使天下后世之人。议吾先生。曰是风流文雅似耆英诸臣可乎。曰是藩邑遗爱似召公可乎。曰是戡定艰乱。似马伏波,郭令公可乎。曰是致太平似周公可乎。曰是似耆老社甲乙某公可乎。曰是能培壅国家根柢于千万年可乎。吾愿先生努力康强而自谋之也。念昔甲申岁。先生之主试汉城发解也。擢泽荣经义第一。自是十馀年。泽荣之所以蒙国士遇。非他门生比。若乃世俗谄谀之辞。非所以事先生也。
年之间。所经历国家安危否泰。所以焦心肝劳筋骸者不一。而发之种种。已如此矣。然而天下之事尚无穷。先生之年尚未耄。而 天子行且复用先生矣。然则泽荣当何以为先生寿。使天下后世之人。议吾先生。曰是风流文雅似耆英诸臣可乎。曰是藩邑遗爱似召公可乎。曰是戡定艰乱。似马伏波,郭令公可乎。曰是致太平似周公可乎。曰是似耆老社甲乙某公可乎。曰是能培壅国家根柢于千万年可乎。吾愿先生努力康强而自谋之也。念昔甲申岁。先生之主试汉城发解也。擢泽荣经义第一。自是十馀年。泽荣之所以蒙国士遇。非他门生比。若乃世俗谄谀之辞。非所以事先生也。万国地志序(代○辛丑)
天下古今之变。其亦异矣哉。古之时人之足迹。不出四海之外。谈地理者。常如隔烟雾见日月。而邹衍裨海九州之说。归之荒唐矣。今则轮舶所行。呼吸之间。能遍大块八万里之全体。而万国之山川人物。皆可目接情交。无复疑阻。人之生于今之世者。其亦可谓快悦矣乎。古之时英雄俊杰之流。争王竞伯于一时者。少者二三国。多不过六七国。然而犹眩于形势。疲于接应。其争竞之具。不过乎弓矢戈剑。而犹且动伏数十万之尸矣。今则强国之环大块而为邻者以百计。合如云雾。散如风雨。虽孙吴诸葛之才。难以尽测其形势谋虑。而争竞之具。名枪巨炮。摧山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8H 页
 岳翻地轴。如普法之战之类。何翅伏尸数十万哉。呜呼。人之生于今之世者。其亦可谓忧畏矣乎。盖尝原之。天地之心好生而已。惟人亦然。四海之内。皆吾同胞也。皆吾所同悦乐者也。而奈之何以万斤之枪千石之炮。日与同胞为仇而糜之烂之哉。此无他。血气蔽之也。然如欲去其血气而就于天理。虽尧舜之圣。不能博施也。其将如之何。吾愿天下之国。各善其治。治均则势均。势均则力均。力均则彼此之间。莫为雌雄而战争自息。然则吾可与天下之人。梯航山海。相往相来。玉帛樽俎。相言相笑。日见其可悦而不见其可忧也。虽然吾又安能使天下之国。各善其治哉。惟吾之国。吾能自主。吾之治。吾能善之。吾之职事。吾能修之。吾之子弟。吾能教之。务以为天下之先而已矣。编辑局旧刊万国地志。而草创未备。局长某病之。招延日语教官数人。译日本人所撰万国地志。既印讫。持示余而请序。余观其书。自地球天体生业社会。以至宗教邦制。无不备载。头脑既显。肯綮随立。信乎其为经营万国者之所发轫。而裨益乎政治者。为不鲜矣。遂以平日胸中所感者书之。以劝学者。
岳翻地轴。如普法之战之类。何翅伏尸数十万哉。呜呼。人之生于今之世者。其亦可谓忧畏矣乎。盖尝原之。天地之心好生而已。惟人亦然。四海之内。皆吾同胞也。皆吾所同悦乐者也。而奈之何以万斤之枪千石之炮。日与同胞为仇而糜之烂之哉。此无他。血气蔽之也。然如欲去其血气而就于天理。虽尧舜之圣。不能博施也。其将如之何。吾愿天下之国。各善其治。治均则势均。势均则力均。力均则彼此之间。莫为雌雄而战争自息。然则吾可与天下之人。梯航山海。相往相来。玉帛樽俎。相言相笑。日见其可悦而不见其可忧也。虽然吾又安能使天下之国。各善其治哉。惟吾之国。吾能自主。吾之治。吾能善之。吾之职事。吾能修之。吾之子弟。吾能教之。务以为天下之先而已矣。编辑局旧刊万国地志。而草创未备。局长某病之。招延日语教官数人。译日本人所撰万国地志。既印讫。持示余而请序。余观其书。自地球天体生业社会。以至宗教邦制。无不备载。头脑既显。肯綮随立。信乎其为经营万国者之所发轫。而裨益乎政治者。为不鲜矣。遂以平日胸中所感者书之。以劝学者。送闵学士观察平北序(癸卯)
平北二十一郡者。古高句丽之西北地也。东川,广开土之所经营。乙支,盖苏文之所驰骛。隋炀帝,唐太宗之所丧师覆兵。号为天下强梗用武之处。则虽以我朝之文治陶铸。而其人之风气。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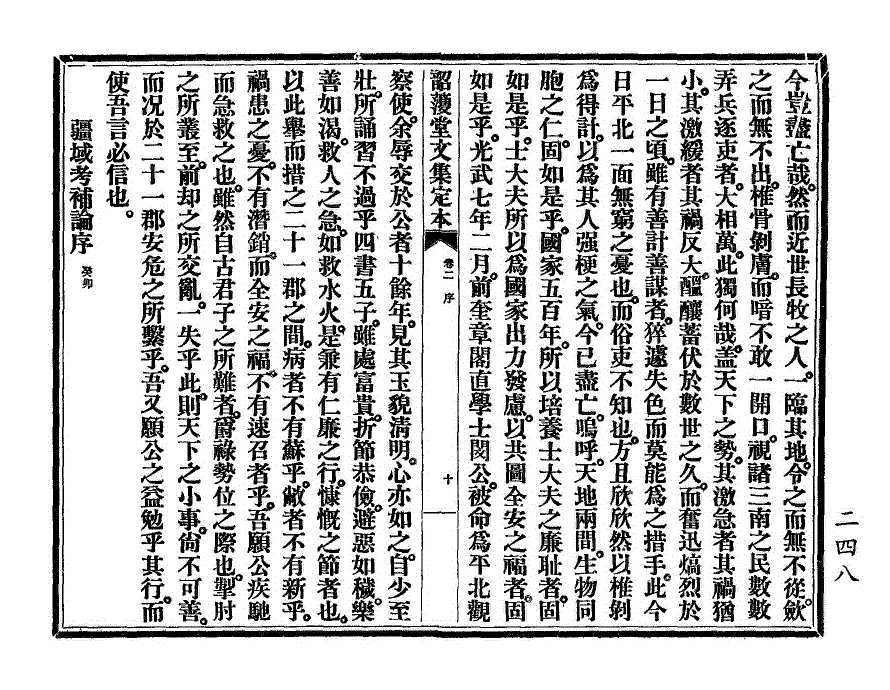 今岂尽亡哉。然而近世长牧之人。一临其地。令之而无不从。敛之而无不出。椎骨剥虏。而喑不敢一开口。视诸三南之民数数弄兵逐吏者。大相万。此独何哉。盖天下之势。其激急者其祸犹小。其激缓者其祸反大。酝酿蓄伏于数世之久。而奋迅熇烈于一日之顷。虽有善计善谋者。猝遽失色而莫能为之措手。此今日平北一面无穷之忧也。而俗吏不知也。方且欣欣然以椎剥为得计。以为其人强梗之气。今已尽亡。呜呼。天地两间。生物同胞之仁。固如是乎。国家五百年。所以培养士大夫之廉耻者。固如是乎。士大夫所以为国家出力发虑。以共图全安之福者。固如是乎。光武七年二月。前奎章阁直学士闵公。被命为平北观察使。余辱交于公者十馀年。见其玉貌清明。心亦如之。自少至壮。所诵习不过乎四书五子。虽处富贵。折节恭俭。避恶如秽。乐善如渴。救人之急。如救水火。是兼有仁廉之行。慷慨之节者也。以此举而措之二十一郡之间。病者不有苏乎。敝者不有新乎。祸患之忧。不有潜销。而全安之福。不有速召者乎。吾愿公疾驰而急救之也。虽然自古君子之所难者。爵禄势位之际也。掣肘之所丛至。前却之所交乱。一失乎此。则天下之小事。尚不可善。而况于二十一郡安危之所系乎。吾又愿公之益勉乎其行。而使吾言必信也。
今岂尽亡哉。然而近世长牧之人。一临其地。令之而无不从。敛之而无不出。椎骨剥虏。而喑不敢一开口。视诸三南之民数数弄兵逐吏者。大相万。此独何哉。盖天下之势。其激急者其祸犹小。其激缓者其祸反大。酝酿蓄伏于数世之久。而奋迅熇烈于一日之顷。虽有善计善谋者。猝遽失色而莫能为之措手。此今日平北一面无穷之忧也。而俗吏不知也。方且欣欣然以椎剥为得计。以为其人强梗之气。今已尽亡。呜呼。天地两间。生物同胞之仁。固如是乎。国家五百年。所以培养士大夫之廉耻者。固如是乎。士大夫所以为国家出力发虑。以共图全安之福者。固如是乎。光武七年二月。前奎章阁直学士闵公。被命为平北观察使。余辱交于公者十馀年。见其玉貌清明。心亦如之。自少至壮。所诵习不过乎四书五子。虽处富贵。折节恭俭。避恶如秽。乐善如渴。救人之急。如救水火。是兼有仁廉之行。慷慨之节者也。以此举而措之二十一郡之间。病者不有苏乎。敝者不有新乎。祸患之忧。不有潜销。而全安之福。不有速召者乎。吾愿公疾驰而急救之也。虽然自古君子之所难者。爵禄势位之际也。掣肘之所丛至。前却之所交乱。一失乎此。则天下之小事。尚不可善。而况于二十一郡安危之所系乎。吾又愿公之益勉乎其行。而使吾言必信也。疆域考补论序(癸卯)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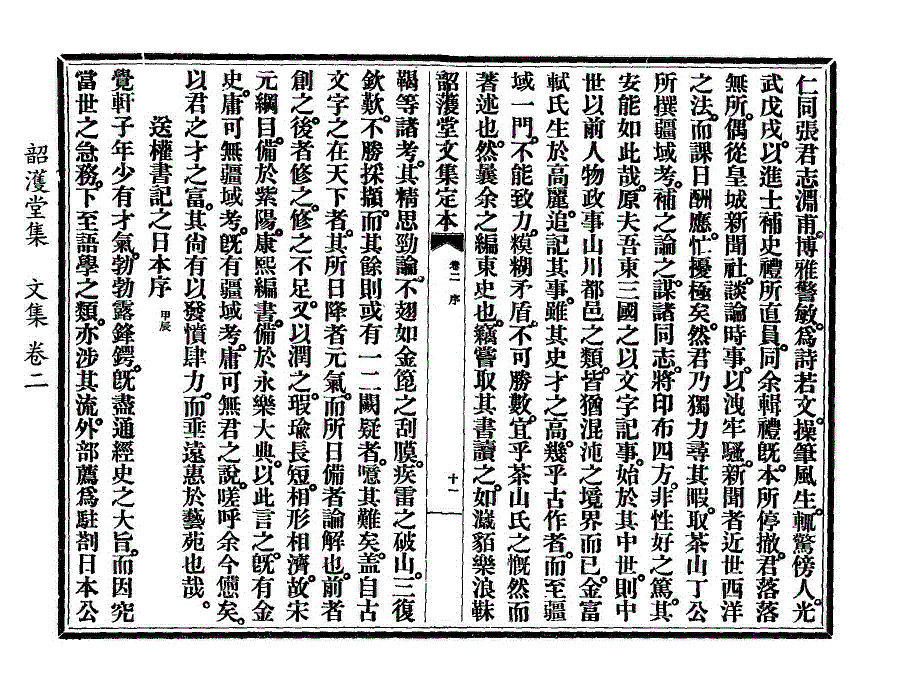 仁同张君志渊甫。博雅警敏。为诗若文。操笔风生。辄惊傍人。光武戊戌。以进士补史礼所直员。同余辑礼既。本所停撤。君落落无所。偶从皇城新闻社。谈论时事。以泄牢骚。新闻者近世西洋之法。而课日酬应。忙扰极矣。然君乃独力寻其暇。取茶山丁公所撰疆域考。补之论之。谋诸同志。将印布四方。非性好之笃。其安能如此哉。原夫吾东三国之以文字记事。始于其中世。则中世以前人物政事山川都邑之类。皆犹混沌之境界而已。金富轼氏生于高丽。追记其事。虽其史才之高。几乎古作者。而至疆域一门。不能致力。模糊矛盾。不可胜数。宜乎茶山氏之慨然而著述也。然曩余之编东史也。窃尝取其书读之。如濊貊乐浪靺鞨等诸考。其精思劲论。不翅如金篦之刮膜。疾雷之破山。三复钦叹。不胜采撷。而其馀则或有一二阙疑者。噫其难矣。盖自古文字之在天下者。其所日降者元气。而所日备者论解也。前者创之。后者修之。修之不足。又以润之。瑕瑜长短。相形相济。故宋元纲目。备于紫阳。康熙编书。备于永乐大典。以此言之。既有金史。庸可无疆域考。既有疆域考。庸可无君之说。嗟呼余今惫矣。以君之才之富。其尚有以发愤肆力。而垂远惠于艺苑也哉。
仁同张君志渊甫。博雅警敏。为诗若文。操笔风生。辄惊傍人。光武戊戌。以进士补史礼所直员。同余辑礼既。本所停撤。君落落无所。偶从皇城新闻社。谈论时事。以泄牢骚。新闻者近世西洋之法。而课日酬应。忙扰极矣。然君乃独力寻其暇。取茶山丁公所撰疆域考。补之论之。谋诸同志。将印布四方。非性好之笃。其安能如此哉。原夫吾东三国之以文字记事。始于其中世。则中世以前人物政事山川都邑之类。皆犹混沌之境界而已。金富轼氏生于高丽。追记其事。虽其史才之高。几乎古作者。而至疆域一门。不能致力。模糊矛盾。不可胜数。宜乎茶山氏之慨然而著述也。然曩余之编东史也。窃尝取其书读之。如濊貊乐浪靺鞨等诸考。其精思劲论。不翅如金篦之刮膜。疾雷之破山。三复钦叹。不胜采撷。而其馀则或有一二阙疑者。噫其难矣。盖自古文字之在天下者。其所日降者元气。而所日备者论解也。前者创之。后者修之。修之不足。又以润之。瑕瑜长短。相形相济。故宋元纲目。备于紫阳。康熙编书。备于永乐大典。以此言之。既有金史。庸可无疆域考。既有疆域考。庸可无君之说。嗟呼余今惫矣。以君之才之富。其尚有以发愤肆力。而垂远惠于艺苑也哉。送权书记之日本序(甲辰)
觉轩子年少有才气。勃勃露锋锷。既尽通经史之大旨。而因究当世之急务。下至语学之类。亦涉其流。外部荐为驻劄日本公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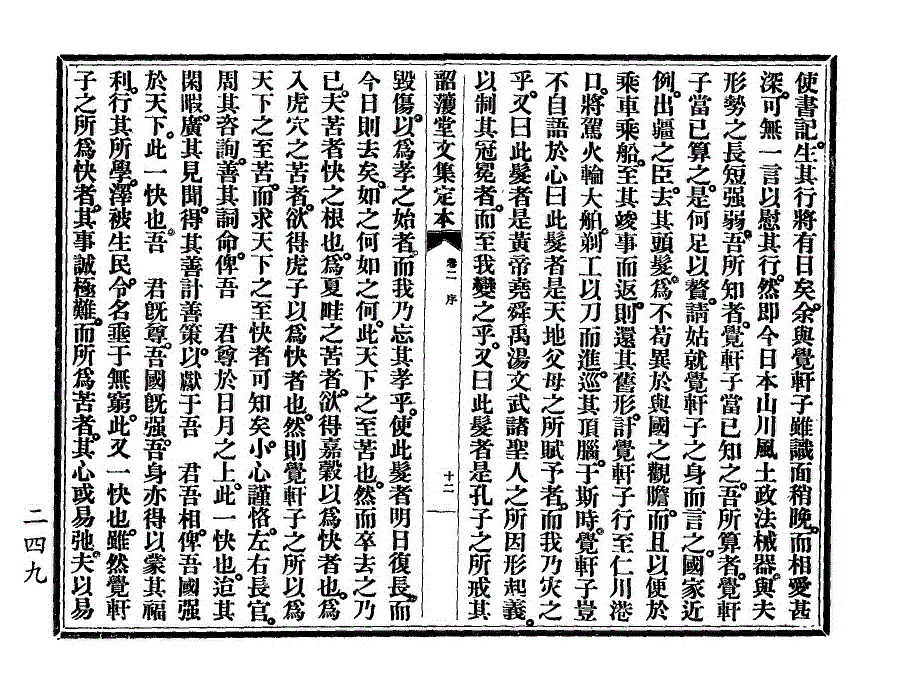 使书记。生其行将有日矣。余与觉轩子虽识面稍晚。而相爱甚深。可无一言以慰其行。然即今日本山川风土政法械器。与夫形势之长短强弱。吾所知者。觉轩子当已知之。吾所算者。觉轩子当已算之。是何足以赘。请姑就觉轩子之身而言之。国家近例。出疆之臣。去其头发。为不苟异于与国之观瞻。而且以便于乘车乘船。至其竣事而返。则还其旧形。计觉轩子行至仁川港口。将驾火轮大舶。剃工以刀而进。巡其顶脑。于斯时。觉轩子岂不自语于心曰此发者是天地父母之所赋予者。而我乃灾之乎。又曰此发者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诸圣人之所因形起义。以制其冠冕者。而至我变之乎。又曰此发者是孔子之所戒其毁伤。以为孝之始者。而我乃忘其孝乎。使此发者明日复长。而今日则去矣。如之何如之何。此天下之至苦也。然而卒去之乃已。夫苦者快之根也。为夏畦之苦者。欲得嘉谷以为快者也。为入虎穴之苦者。欲得虎子以为快者也。然则觉轩子之所以为天下之至苦。而求天下之至快者可知矣。小心谨恪。左右长官。周其咨询。善其词命。俾吾 君尊于日月之上。此一快也。迨其闲暇。广其见闻。得其善计善策。以献于吾 君吾相。俾吾国强于天下。此一快也。吾 君既尊。吾国既强。吾身亦得以蒙其福利。行其所学。泽被生民。令名垂于无穷。此又一快也。虽然觉轩子之所为快者。其事诚极难。而所为苦者。其心或易弛。夫以易
使书记。生其行将有日矣。余与觉轩子虽识面稍晚。而相爱甚深。可无一言以慰其行。然即今日本山川风土政法械器。与夫形势之长短强弱。吾所知者。觉轩子当已知之。吾所算者。觉轩子当已算之。是何足以赘。请姑就觉轩子之身而言之。国家近例。出疆之臣。去其头发。为不苟异于与国之观瞻。而且以便于乘车乘船。至其竣事而返。则还其旧形。计觉轩子行至仁川港口。将驾火轮大舶。剃工以刀而进。巡其顶脑。于斯时。觉轩子岂不自语于心曰此发者是天地父母之所赋予者。而我乃灾之乎。又曰此发者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诸圣人之所因形起义。以制其冠冕者。而至我变之乎。又曰此发者是孔子之所戒其毁伤。以为孝之始者。而我乃忘其孝乎。使此发者明日复长。而今日则去矣。如之何如之何。此天下之至苦也。然而卒去之乃已。夫苦者快之根也。为夏畦之苦者。欲得嘉谷以为快者也。为入虎穴之苦者。欲得虎子以为快者也。然则觉轩子之所以为天下之至苦。而求天下之至快者可知矣。小心谨恪。左右长官。周其咨询。善其词命。俾吾 君尊于日月之上。此一快也。迨其闲暇。广其见闻。得其善计善策。以献于吾 君吾相。俾吾国强于天下。此一快也。吾 君既尊。吾国既强。吾身亦得以蒙其福利。行其所学。泽被生民。令名垂于无穷。此又一快也。虽然觉轩子之所为快者。其事诚极难。而所为苦者。其心或易弛。夫以易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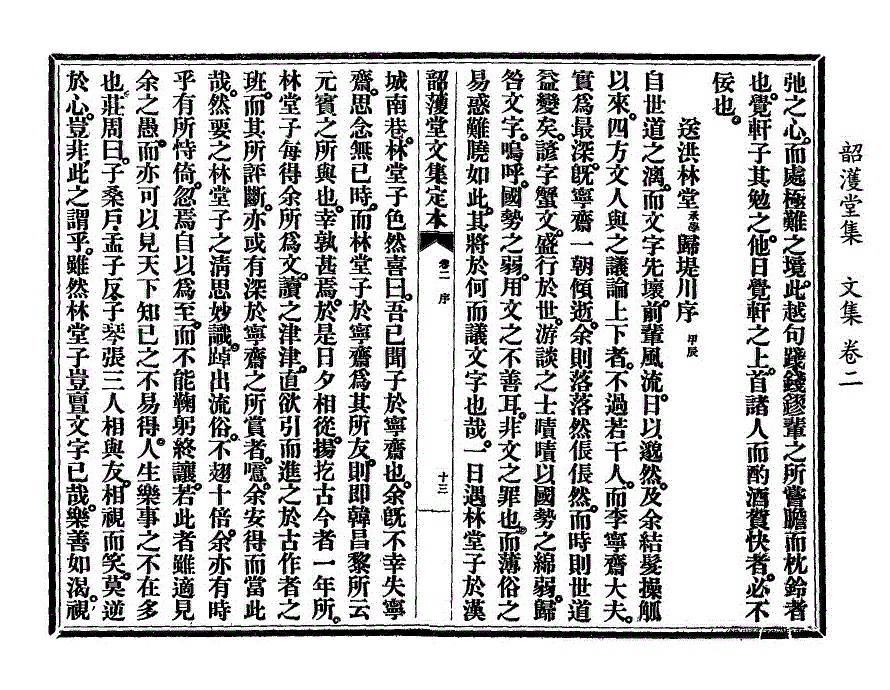 弛之心。而处极难之境。此越句践,钱镠辈之所尝胆而枕铃者也。觉轩子其勉之。他日觉轩之上。首诸人而酌酒贺快者。必不佞也。
弛之心。而处极难之境。此越句践,钱镠辈之所尝胆而枕铃者也。觉轩子其勉之。他日觉轩之上。首诸人而酌酒贺快者。必不佞也。送洪林堂(承学)归堤川序(甲辰)
自世道之漓。而文字先坏。前辈风流。日以邈然。及余结发操觚以来。四方文人与之议论上下者。不过若干人。而李宁斋大夫。实为最深。既宁斋一朝倾逝。余则落落然伥伥然。而时则世道益变矣。谚字蟹文。盛行于世。游谈之士啧啧以国势之绵弱。归咎文字。呜呼。国势之弱。用文之不善耳。非文之罪也。而薄俗之易惑难晓如此。其将于何而议文字也哉。一日遇林堂子于汉城南巷。林堂子色然喜曰。吾已闻子于宁斋也。余既不幸失宁斋。思念无已时。而林堂子于宁斋为其所友。则即韩昌黎所云元宾之所与也。幸孰甚焉。于是日夕相从。扬扢古今者一年所。林堂子每得余所为文。读之津津。直欲引而进之于古作者之班。而其所评断。亦或有深于宁斋之所赏者。噫。余安得而当此哉。然要之林堂子之清思妙识。踔出流俗。不翅十倍。余亦有时乎有所恃倚。忽焉自以为至。而不能鞠躬终让。若此者虽适见余之愚。而亦可以见天下知己之不易得。人生乐事之不在多也。庄周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岂非此之谓乎。虽然林堂子岂亶文字已哉。乐善如渴。视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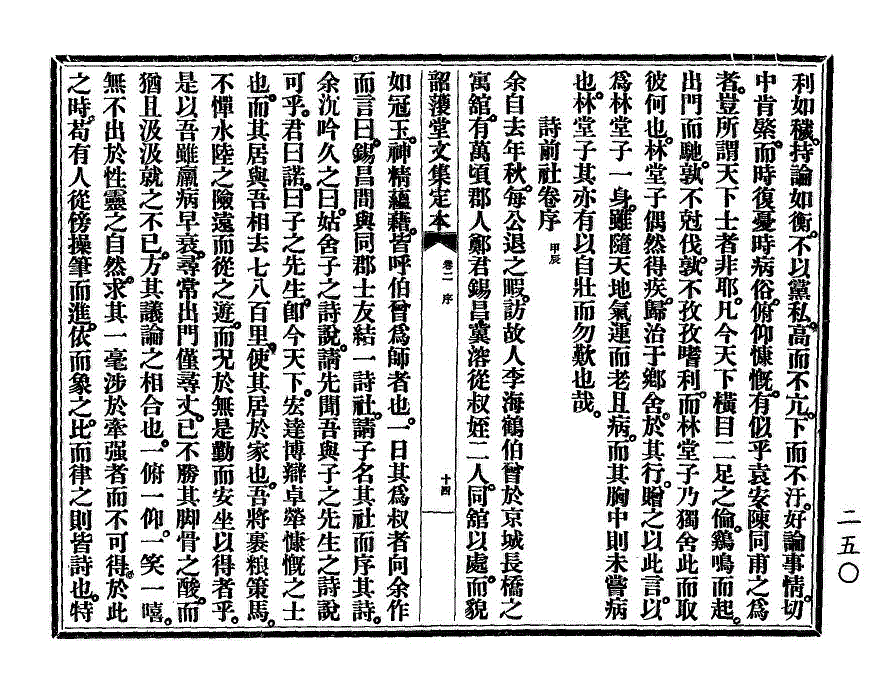 利如秽。持论如衡。不以党私。高而不亢。下而不污。好论事情。切中肯綮。而时复忧时病俗。俯仰慷慨。有似乎袁安,陈同甫之为者。岂所谓天下士者非耶。凡今天下横目二足之伦。鸡鸣而起。出门而驰。孰不尅伐。孰不孜孜嗜利。而林堂子乃独舍此而取彼何也。林堂子偶然得疾。归治于乡舍。于其行。赠之以此言。以为林堂子一身。虽随天地气运而老且病。而其胸中则未尝病也。林堂子其亦有以自壮而勿叹也哉。
利如秽。持论如衡。不以党私。高而不亢。下而不污。好论事情。切中肯綮。而时复忧时病俗。俯仰慷慨。有似乎袁安,陈同甫之为者。岂所谓天下士者非耶。凡今天下横目二足之伦。鸡鸣而起。出门而驰。孰不尅伐。孰不孜孜嗜利。而林堂子乃独舍此而取彼何也。林堂子偶然得疾。归治于乡舍。于其行。赠之以此言。以为林堂子一身。虽随天地气运而老且病。而其胸中则未尝病也。林堂子其亦有以自壮而勿叹也哉。诗前社卷序(甲辰)
余自去年秋。每公退之暇。访故人李海鹤伯曾于京城长桥之寓馆。有万顷郡人郑君锡昌,冀溶从叔侄二人。同馆以处。而貌如冠玉。神精蕴藉。皆呼伯曾为师者也。一日其为叔者向余作而言曰。锡昌间与同郡士友结一诗社。请子名其社而序其诗。余沉吟久之曰。姑舍子之诗说。请先闻吾与子之先生之诗说可乎。君曰诺。曰子之先生。即今天下。宏达博辩卓荦慷慨之士也。而其居与吾相去七八百里。使其居于家也。吾将裹粮策马。不惮水陆之险远而从之游。而况于无是勤而安坐以得者乎。是以吾虽羸病早衰。寻常出门仅寻丈。已不胜其脚骨之酸。而犹且汲汲就之不已。方其议论之相合也。一俯一仰。一笑一嘻。无不出于性灵之自然。求其一毫涉于牵强者而不可得。于此之时。苟有人从傍操笔而进。依而象之。比而律之则皆诗也。特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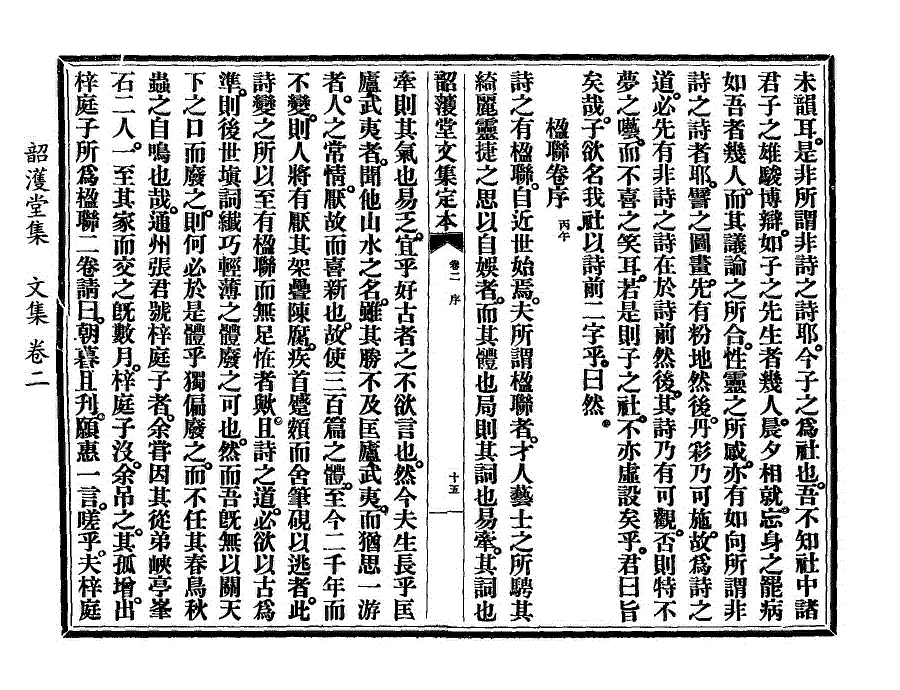 未韵耳。是非所谓非诗之诗耶。今子之为社也。吾不知社中诸君子之雄骏博辩。如子之先生者几人。晨夕相就。忘身之罢病如吾者几人。而其议论之所合。性灵之所感。亦有如向所谓非诗之诗者耶。譬之图画。先有粉地然后。丹彩乃可施。故为诗之道。必先有非诗之诗在于诗前然后。其诗乃有可观。否则特不梦之呓。而不喜之笑耳。若是则子之社。不亦虚设矣乎。君曰旨矣哉。子欲名我社以诗前二字乎。曰然。
未韵耳。是非所谓非诗之诗耶。今子之为社也。吾不知社中诸君子之雄骏博辩。如子之先生者几人。晨夕相就。忘身之罢病如吾者几人。而其议论之所合。性灵之所感。亦有如向所谓非诗之诗者耶。譬之图画。先有粉地然后。丹彩乃可施。故为诗之道。必先有非诗之诗在于诗前然后。其诗乃有可观。否则特不梦之呓。而不喜之笑耳。若是则子之社。不亦虚设矣乎。君曰旨矣哉。子欲名我社以诗前二字乎。曰然。楹联卷序(丙午)
诗之有楹联。自近世始焉。夫所谓楹联者。才人艺士之所骋其绮丽灵捷之思以自娱者。而其体也局则其词也易牵。其词也牵则其气也易乏。宜乎好古者之不欲言也。然今夫生长乎匡庐,武夷者。闻他山水之名。虽其胜不及匡庐,武夷。而犹思一游者。人之常情。厌故而喜新也。故使三百篇之体。至今二千年而不变。则人将有厌其架叠陈腐。疾首蹙頞而舍笔砚以逃者。此诗变之所以至有楹联而无足怪者欤。且诗之道。必欲以古为准。则后世填词纤巧轻薄之体废之可也。然而吾既无以关天下之口而废之。则何必于是体乎独偏废之。而不任其春鸟秋虫之自鸣也哉。通州张君号梓庭子者。余尝因其从弟峡亭峰石二人。一至其家而交之既数月。梓庭子没。余吊之。其孤增。出梓庭子所为楹联二卷请曰。朝暮且刊。愿惠一言。嗟乎。夫梓庭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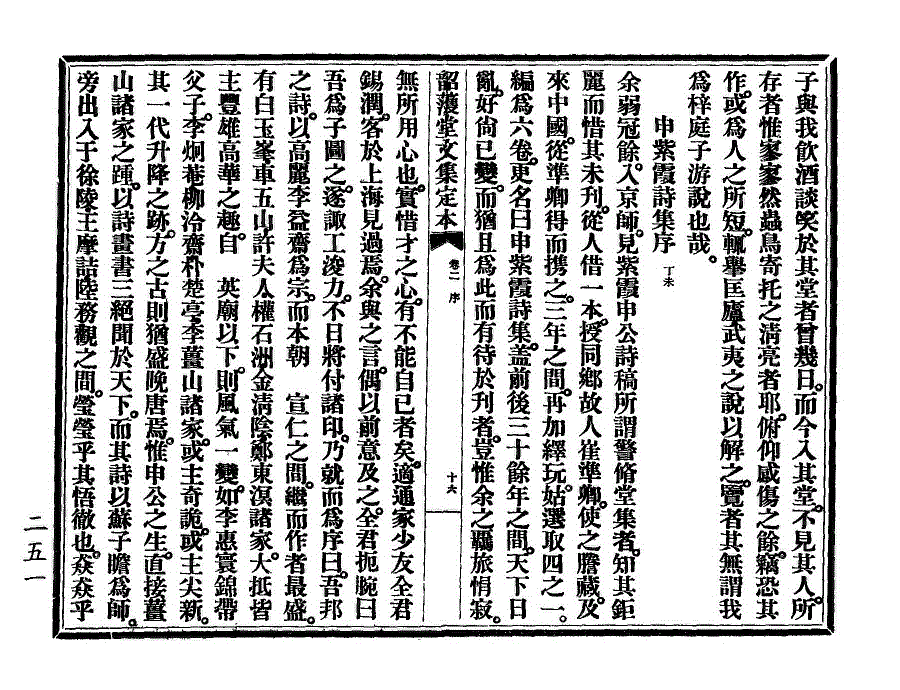 子与我饮酒谈笑于其堂者曾几日。而今入其堂。不见其人。所存者惟寥寥然虫鸟寄托之清亮者耶。俯仰感伤之馀。窃恐其作。或为人之所短。辄举匡庐,武夷之说以解之。览者其无谓我为梓庭子游说也哉。
子与我饮酒谈笑于其堂者曾几日。而今入其堂。不见其人。所存者惟寥寥然虫鸟寄托之清亮者耶。俯仰感伤之馀。窃恐其作。或为人之所短。辄举匡庐,武夷之说以解之。览者其无谓我为梓庭子游说也哉。申紫霞诗集序(丁未)
余弱冠馀。入京师。见紫霞申公诗稿所谓警脩堂集者。知其钜丽而惜其未刊。从人借一本。授同乡故人崔准卿。使之誊藏。及来中国。从准卿得而携之。三年之间。再加绎玩。姑选取四之一。编为六卷。更名曰申紫霞诗集。盖前后三十馀年之间。天下日乱。好尚已变。而犹且为此而有待于刊者。岂惟余之羁旅悁寂。无所用心也。实惜才之心。有不能自已者矣。适通家少友全君锡润。客于上海见过焉。余与之言。偶以前意及之。全君扼腕曰吾为子图之。遂诹工浚力。不日将付诸印。乃就而为序曰。吾邦之诗。以高丽李益斋为宗。而本朝 宣仁之间。继而作者最盛。有白玉峰,车五山,许夫人,权石洲,金清阴,郑东溟诸家。大抵皆主丰雄高华之趣。自 英庙以下。则风气一变。如李惠寰锦带父子。李炯庵,柳泠斋,朴楚亭,李姜山诸家。或主奇诡。或主尖新。其一代升降之迹。方之古则犹盛晚唐焉。惟申公之生。直接姜山诸家之踵。以诗画书三绝闻于天下。而其诗以苏子瞻为师。旁出入于徐陵,王摩诘,陆务观之间。莹莹乎其悟彻也。猋猋乎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2H 页
 其驰突也。能艳能野。能幻能实。能拙能豪。能平能险。千情万状。随意牢笼。无不活动。森在目前。使读者目眩神醉。如万舞之方张。五齐之方醲。可谓具旷世之奇才。穷一代之极变。而翩翩乎其衰晚之大家者矣。庸不盛哉。抑有异者。公之同时前辈。有曰朴燕岩先生者。其文在本邦古文家中。出类拔萃。变动具万象。与公之诗。对为两豪。岂天之生物。有龙则必有虎。有珠则必有玉之类欤。聊附此论以告一世。
其驰突也。能艳能野。能幻能实。能拙能豪。能平能险。千情万状。随意牢笼。无不活动。森在目前。使读者目眩神醉。如万舞之方张。五齐之方醲。可谓具旷世之奇才。穷一代之极变。而翩翩乎其衰晚之大家者矣。庸不盛哉。抑有异者。公之同时前辈。有曰朴燕岩先生者。其文在本邦古文家中。出类拔萃。变动具万象。与公之诗。对为两豪。岂天之生物。有龙则必有虎。有珠则必有玉之类欤。聊附此论以告一世。张退翁六十寿序(庚戌)
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惑也。泽荣尝读而解之曰。爱欲其生。情之顺也。岂为惑也。夫子之所谓惑者。指其欲生于不可生者也。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然则不可生者。即其不直者耳。如使天下有人焉。能持直道以行。而吾从而爱其人而欲其生。则夫子之不谓惑也决矣。吾友清国通州张退庵先生。有闳明简坚之质。少与其弟啬庵殿撰公同苦学。有文字之清识。翰墨之妙力。既而急于奉老。辍书干蛊。以笃成殿撰之学。中年为吴武壮公所知。比武壮之援吾韩也。与殿撰同参军事。用其劳摄江西数县。治平皆为天下最。奖除宜春知县。朝夕将大畀。会殿撰以中国困于外侮。思教育人才而无其力。先营实业。先生闻之。悯其孤劳。解印而归省抚。力挽而终不听。遂助实业。以兴学校。其他农务荒政。河渠道路。一切公益之事。亦莫不与殿撰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2L 页
 协担。州里赖之。今年九月三十日。为其六十岁之生辰。其子郎中君。将以其日设宴称寿。殿撰弟子婺源江君敬持以先生政略一通抵泽荣曰。子可据此以寿先生乎。始先生兄弟之来吾韩也。泽荣得以交驩。近而有所不乐。挈孥遁逃。以累先生兄弟者。今且六阅寒暑。则此其情于先生为爱乎否也。其爱之之由。余可姑勿毕言。苟有有心君子阅天下之书者。闻此而想像之。则其或将代余而毕言矣乎。虽然董卓之于蔡伯喈也。虽能使之感激。而其身不能直矣。今先生则不然。于家则为人之孝子慈兄。于乡则为人之耆德。于郡县则为人之贤官。于公益则为人之义民。凡其所为。无一之不直。则吾之爱之。岂非情之正。而于以祝其久生于世也。岂为惑哉。吾愿先生自今三数十年。康强无恙。以与殿撰。卒收教育之成效也。噫夫其三数十年之间。而教育之效成。则是不仅先生寿也。即凡中国罢病之人。庶几赖以得寿。而其馀波亦可以及于吾韩。此尤余之所大愿欲也。敢不执觞以待。
协担。州里赖之。今年九月三十日。为其六十岁之生辰。其子郎中君。将以其日设宴称寿。殿撰弟子婺源江君敬持以先生政略一通抵泽荣曰。子可据此以寿先生乎。始先生兄弟之来吾韩也。泽荣得以交驩。近而有所不乐。挈孥遁逃。以累先生兄弟者。今且六阅寒暑。则此其情于先生为爱乎否也。其爱之之由。余可姑勿毕言。苟有有心君子阅天下之书者。闻此而想像之。则其或将代余而毕言矣乎。虽然董卓之于蔡伯喈也。虽能使之感激。而其身不能直矣。今先生则不然。于家则为人之孝子慈兄。于乡则为人之耆德。于郡县则为人之贤官。于公益则为人之义民。凡其所为。无一之不直。则吾之爱之。岂非情之正。而于以祝其久生于世也。岂为惑哉。吾愿先生自今三数十年。康强无恙。以与殿撰。卒收教育之成效也。噫夫其三数十年之间。而教育之效成。则是不仅先生寿也。即凡中国罢病之人。庶几赖以得寿。而其馀波亦可以及于吾韩。此尤余之所大愿欲也。敢不执觞以待。惜馀春轩诗草序(庚戌)
有善刻金石而游于翰墨林书局者曰宋生延年。日持其先大人贡生金绶君诗。请曰择与序。敢并勤子。余受而择之已。谓生曰。子之先人之诗。子将何以尊诸。生戚然言曰。将世之乎。则吾之先人不幸短年。学未充才。将家之乎。则吾又不可以请子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3H 页
 作。二者莫知所以为图。所谓我乃行之。反求不得吾心者也。曰子其安哉。以欲世者而家之。则必益勤于藏守而孝道存焉。以欲家者而世之。则必不滥求其人誉而直道存焉。不家不世之间。孝经春秋之道。并行而不悖。吾诚乐闻其事矣。有不沛然于言者乎。
作。二者莫知所以为图。所谓我乃行之。反求不得吾心者也。曰子其安哉。以欲世者而家之。则必益勤于藏守而孝道存焉。以欲家者而世之。则必不滥求其人誉而直道存焉。不家不世之间。孝经春秋之道。并行而不悖。吾诚乐闻其事矣。有不沛然于言者乎。张啬翁六十寿序(壬子)
中华民国之初。天下议者曰。盐政之敝久矣。张啬翁宜为盐。于是翁被选为盐政总理。视事者数月。而适届六十岁之诞辰。即壬子五月二十五日也。翁之兄退翁。左展老子骑牛出关图。而右觞之曰吾弟寿哉。翁辞曰未敢以为乐也。天下尚未平。其子怡祖及弟子江谦等。以至所私育师范学校生徒五六百人。或拜或跪。或鹄立而列侍。无不凝目伺其手之至觞者。其馆客韩遗民金泽荣。方病在床。闻其事。为之致辞曰。甚矣翁之忧深思远也。夫以泽荣之俘虏之漏网者。而视今日之中国。犹嫠者之见人新婚。方且羡之之不暇。而翁乃尚以为未平蹙蹙焉。若不可以一日乐乎。虽然翁之寿其在是乎。自生民来。有才者未必有心。有心者未必有才。二者之难全久矣。今翁学术之宏。可以笼万汇矣。文章翰墨之劲。可以沮金石而骇鬼物矣。而尤邃于经济。其度事而措物。秋毫之析也。夜室之执烛也。城门之轨。而王良,造父。良驭者之驱也。潜光伏彩于江海之间农贾之班。而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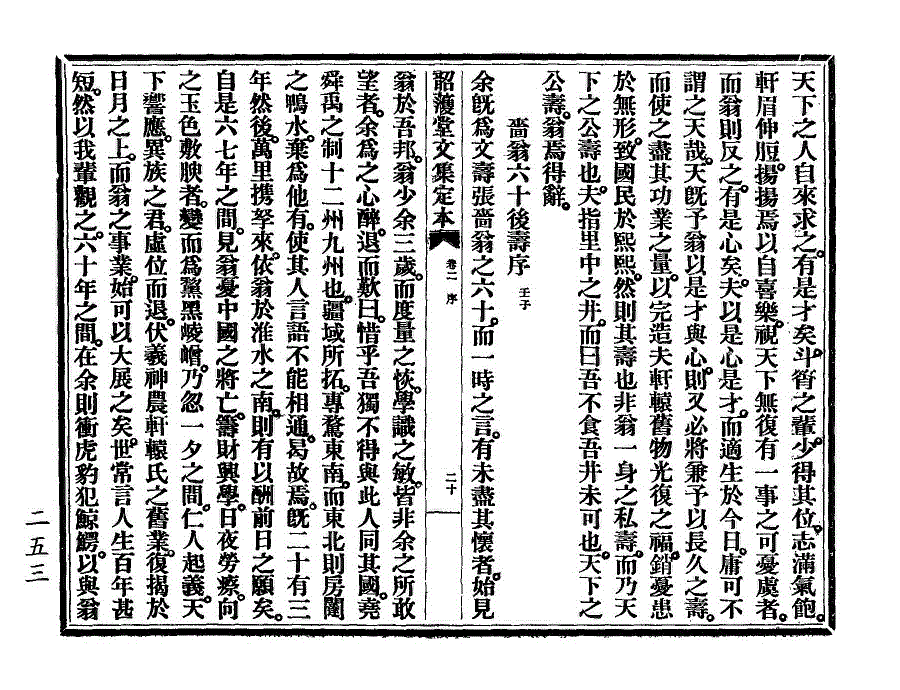 天下之人自来求之。有是才矣。斗筲之辈。少得其位。志满气饱。轩眉伸脰。扬扬焉以自喜乐。视天下无复有一事之可忧虞者。而翁则反之。有是心矣。夫以是心是才。而适生于今日。庸可不谓之天哉。天既予翁以是才与心。则又必将兼予以长久之寿。而使之尽其功业之量。以完造夫轩辕旧物光复之福。销忧患于无形。致国民于熙熙。然则其寿也非翁一身之私寿。而乃天下之公寿也。夫指里中之井。而曰吾不食吾井未可也。天下之公寿。翁焉得辞。
天下之人自来求之。有是才矣。斗筲之辈。少得其位。志满气饱。轩眉伸脰。扬扬焉以自喜乐。视天下无复有一事之可忧虞者。而翁则反之。有是心矣。夫以是心是才。而适生于今日。庸可不谓之天哉。天既予翁以是才与心。则又必将兼予以长久之寿。而使之尽其功业之量。以完造夫轩辕旧物光复之福。销忧患于无形。致国民于熙熙。然则其寿也非翁一身之私寿。而乃天下之公寿也。夫指里中之井。而曰吾不食吾井未可也。天下之公寿。翁焉得辞。啬翁六十后寿序(壬子)
余既为文寿张啬翁之六十。而一时之言。有未尽其怀者。始见翁于吾邦。翁少余三岁。而度量之恢。学识之敏。皆非余之所敢望者。余为之心醉。退而叹曰。惜乎吾独不得与此人同其国。尧舜禹之制十二州九州也。疆域所拓。专骛东南。而东北则房闼之鸭水。弃为他有。使其人言语不能相通。曷故焉。既二十有三年然后。万里携孥来。依翁于淮水之南。则有以酬前日之愿矣。自是六七年之间。见翁忧中国之将亡。筹财兴学。日夜劳瘵。向之玉色敷腴者。变而为黧黑崚嶒。乃忽一夕之间。仁人起义。天下响应。异族之君。虚位而退。伏羲神农轩辕氏之旧业。复揭于日月之上。而翁之事业。始可以大展之矣。世常言人生百年甚短。然以我辈观之。六十年之间。在余则冲虎豹犯鲸鳄。以与翁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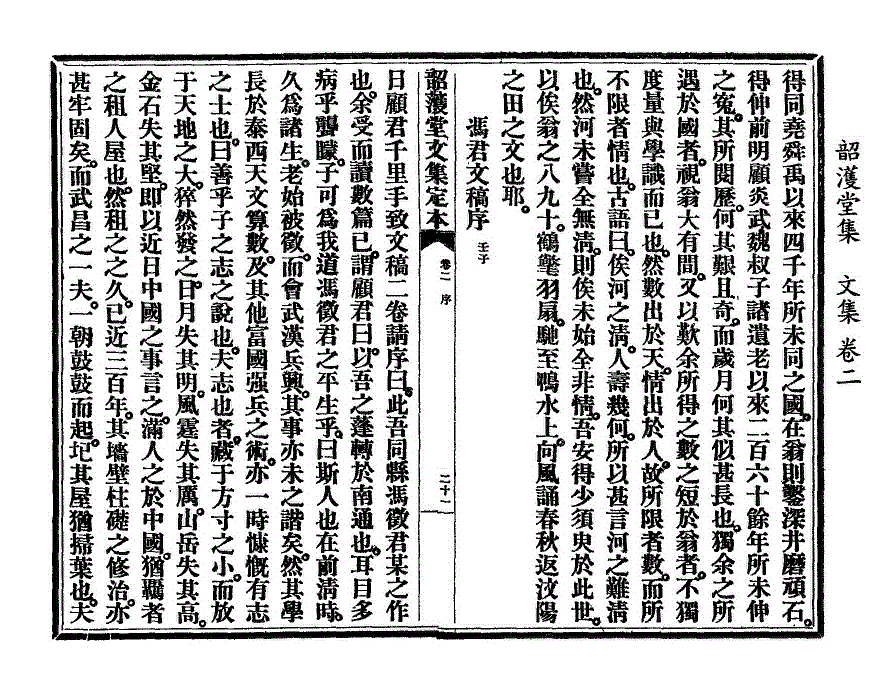 得同尧舜禹以来四千年所未同之国。在翁则凿深井磨顽石。得伸前明顾炎武,魏叔子诸遗老以来二百六十馀年所未伸之冤。其所阅历。何其艰且奇。而岁月何其似甚长也。独余之所遇于国者。视翁大有间。又以叹余所得之数之短于翁者。不独度量与学识而已也。然数出于天。情出于人。故所限者数。而所不限者情也。古语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所以甚言河之难清也。然河未尝全无清。则俟未始全非情。吾安得少须臾于此世。以俟翁之八九十。鹤氅羽扇。驰至鸭水上。向风诵春秋返汶阳之田之文也耶。
得同尧舜禹以来四千年所未同之国。在翁则凿深井磨顽石。得伸前明顾炎武,魏叔子诸遗老以来二百六十馀年所未伸之冤。其所阅历。何其艰且奇。而岁月何其似甚长也。独余之所遇于国者。视翁大有间。又以叹余所得之数之短于翁者。不独度量与学识而已也。然数出于天。情出于人。故所限者数。而所不限者情也。古语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所以甚言河之难清也。然河未尝全无清。则俟未始全非情。吾安得少须臾于此世。以俟翁之八九十。鹤氅羽扇。驰至鸭水上。向风诵春秋返汶阳之田之文也耶。冯君文稿序(壬子)
日顾君千里手致文稿二卷请序曰。此吾同县冯徵君某之作也。余受而读数篇已。谓顾君曰。以吾之蓬转于南通也。耳目多病乎聋矇。子可为我道冯徵君之平生乎。曰斯人也在前清时。久为诸生。老始被徵。而会武汉兵兴。其事亦未之谐矣。然其学长于泰西天文算数。及其他富国强兵之术。亦一时慷慨有志之士也。曰善乎子之志之说也。夫志也者。藏于方寸之小。而放于天地之大。猝然发之。日月失其明。风霆失其厉。山岳失其高。金石失其坚。即以近日中国之事言之。满人之于中国。犹羁者之租人屋也。然租之之久。已近三百年。其墙壁柱础之修治。亦甚牢固矣。而武昌之一夫。一朝鼓鼓而起。圮其屋犹扫叶也。夫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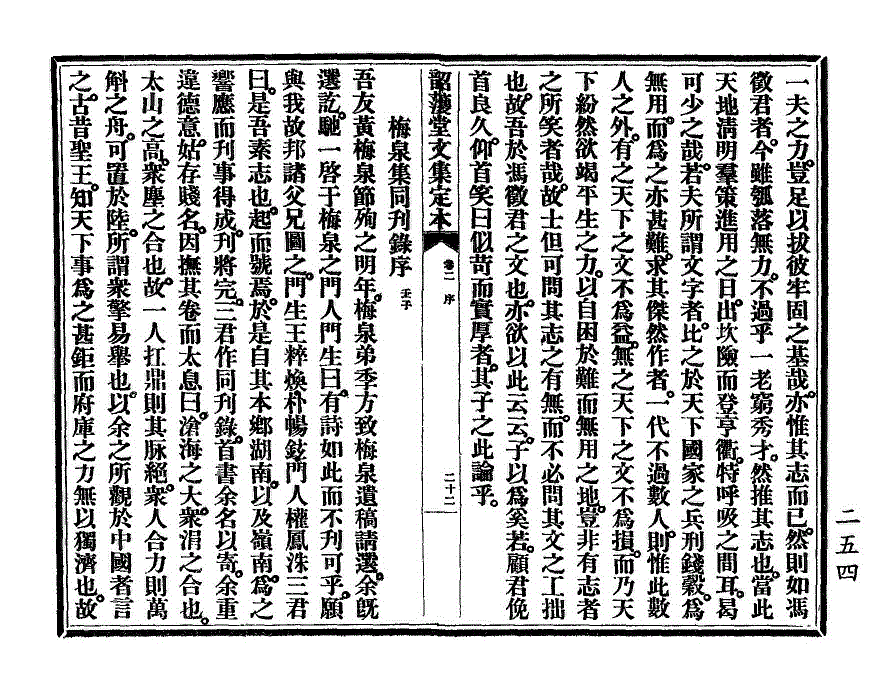 一夫之力。岂足以拔彼牢固之基哉。亦惟其志而已。然则如冯徵君者。今虽瓠落无力。不过乎一老穷秀才。然推其志也。当此天地清明群策进用之日。出坎险而登亨衢。特呼吸之间耳。曷可少之哉。若夫所谓文字者。比之于天下国家之兵刑钱谷。为无用。而为之亦甚难。求其杰然作者。一代不过数人。则惟此数人之外。有之天下之文不为益。无之天下之文不为损。而乃天下纷然欲竭平生之力。以自困于难而无用之地。岂非有志者之所笑者哉。故士但可问其志之有无。而不必问其文之工拙也。故吾于冯徵君之文也。亦欲以此云云。子以为奚若。顾君俛首良久。仰首笑曰似苛而实厚者。其子之此论乎。
一夫之力。岂足以拔彼牢固之基哉。亦惟其志而已。然则如冯徵君者。今虽瓠落无力。不过乎一老穷秀才。然推其志也。当此天地清明群策进用之日。出坎险而登亨衢。特呼吸之间耳。曷可少之哉。若夫所谓文字者。比之于天下国家之兵刑钱谷。为无用。而为之亦甚难。求其杰然作者。一代不过数人。则惟此数人之外。有之天下之文不为益。无之天下之文不为损。而乃天下纷然欲竭平生之力。以自困于难而无用之地。岂非有志者之所笑者哉。故士但可问其志之有无。而不必问其文之工拙也。故吾于冯徵君之文也。亦欲以此云云。子以为奚若。顾君俛首良久。仰首笑曰似苛而实厚者。其子之此论乎。梅泉集同刊录序(壬子)
吾友黄梅泉节殉之明年。梅泉弟季方致梅泉遗稿请选。余既选讫。驰一启于梅泉之门人门生曰。有诗如此而不刊可乎。愿与我故邦诸父兄图之。门生王粹焕,朴畅铉,门人权凤洙三君曰。是吾素志也。起而号焉。于是自其本乡湖南。以及岭南。为之响应而刊事得成。刊将完。三君作同刊录。首书余名以寄。余重违德意。姑存贱名。因抚其卷而太息曰。沧海之大。众涓之合也。太山之高。众尘之合也。故一人扛鼎则其脉绝。众人合力则万斛之舟。可置于陆。所谓众擎易举也。以余之所观于中国者言之。古昔圣王。知天下事为之甚钜而府库之力无以独济也。故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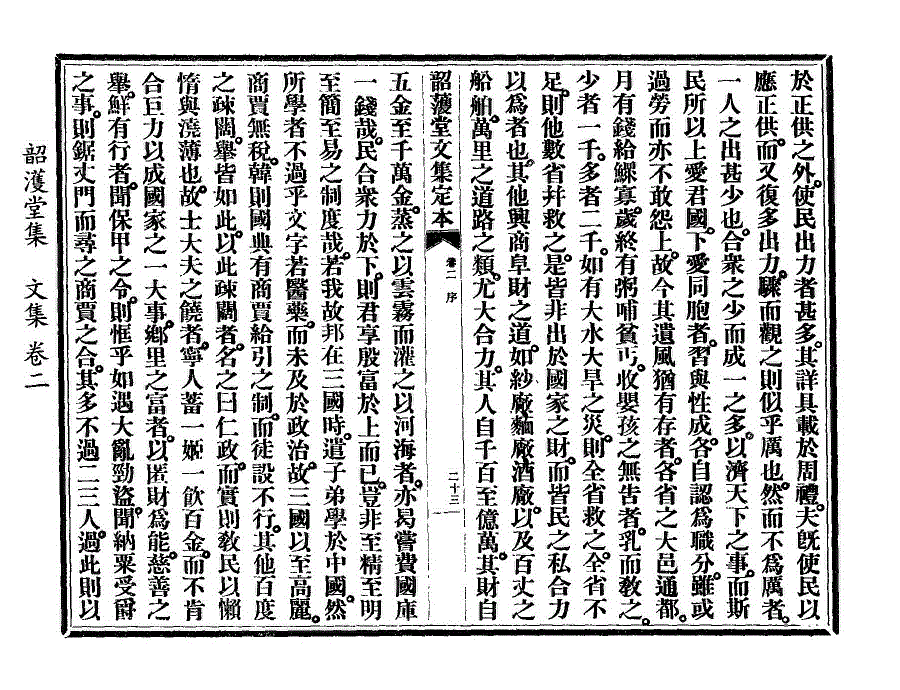 于正供之外。使民出力者甚多。其详具载于周礼。夫既使民以应正供。而又复多出力。骤而观之则似乎厉也。然而不为厉者。一人之出甚少也。合众之少而成一之多。以济天下之事。而斯民所以上爱君国。下爱同胞者。习与性成。各自认为职分。虽或过劳而亦不敢怨上。故今其遗风犹有存者。各省之大邑通都。月有钱给鳏寡。岁终有粥哺贫丐。收婴孩之无告者。乳而教之。少者一千。多者二千。如有大水大旱之灾。则全省救之。全省不足。则他数省并救之。是皆非出于国家之财。而皆民之私合力以为者也。其他兴商阜财之道。如纱厂,面厂,酒厂。以及百丈之船舶。万里之道路之类。尤大合力。其人自千百至亿万。其财自五金至千万金。蒸之以云雾而灌之以河海者。亦曷尝费国库一钱哉。民合众力于下。则君享殷富于上而已。岂非至精至明至简至易之制度哉。若我故邦在三国时。遣子弟学于中国。然所学者不过乎文字若医药。而未及于政治。故三国以至高丽。商贾无税。韩则国典有商贾给引之制。而徒设不行。其他百度之疏阔。举皆如此。以此疏阔者。名之曰仁政。而实则教民以懒惰与浇薄也。故士大夫之饶者。宁人蓄一姬一饮百金。而不肯合巨力以成国家之一大事。乡里之富者。以匿财为能。慈善之举。鲜有行者。闻保甲之令。则恇乎如遇大乱劲盗。闻纳粟受爵之事。则锯丈门而寻之商贾之合。其多不过二三人。过此则以
于正供之外。使民出力者甚多。其详具载于周礼。夫既使民以应正供。而又复多出力。骤而观之则似乎厉也。然而不为厉者。一人之出甚少也。合众之少而成一之多。以济天下之事。而斯民所以上爱君国。下爱同胞者。习与性成。各自认为职分。虽或过劳而亦不敢怨上。故今其遗风犹有存者。各省之大邑通都。月有钱给鳏寡。岁终有粥哺贫丐。收婴孩之无告者。乳而教之。少者一千。多者二千。如有大水大旱之灾。则全省救之。全省不足。则他数省并救之。是皆非出于国家之财。而皆民之私合力以为者也。其他兴商阜财之道。如纱厂,面厂,酒厂。以及百丈之船舶。万里之道路之类。尤大合力。其人自千百至亿万。其财自五金至千万金。蒸之以云雾而灌之以河海者。亦曷尝费国库一钱哉。民合众力于下。则君享殷富于上而已。岂非至精至明至简至易之制度哉。若我故邦在三国时。遣子弟学于中国。然所学者不过乎文字若医药。而未及于政治。故三国以至高丽。商贾无税。韩则国典有商贾给引之制。而徒设不行。其他百度之疏阔。举皆如此。以此疏阔者。名之曰仁政。而实则教民以懒惰与浇薄也。故士大夫之饶者。宁人蓄一姬一饮百金。而不肯合巨力以成国家之一大事。乡里之富者。以匿财为能。慈善之举。鲜有行者。闻保甲之令。则恇乎如遇大乱劲盗。闻纳粟受爵之事。则锯丈门而寻之商贾之合。其多不过二三人。过此则以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二 第 255L 页
 无律章之防也。奸蠹横出。遂以破败而止。于是乎零丁孤孑。贫窳枯槁。万事无一可济。而遂至于今日矣。呜呼。凡人之丧。追言饮食药饵之失。宜无益于已死者。而犹不能不言者。人之情也。然则今于故邦之事。独无是之情哉。故辄因梅泉集之事之感。而献中国之说于吾故邦诸父兄。以为他日故邦之事有大于是集者。则以是集之所以成者为师。即中国之说也。虽然独止是哉。独止是哉。
无律章之防也。奸蠹横出。遂以破败而止。于是乎零丁孤孑。贫窳枯槁。万事无一可济。而遂至于今日矣。呜呼。凡人之丧。追言饮食药饵之失。宜无益于已死者。而犹不能不言者。人之情也。然则今于故邦之事。独无是之情哉。故辄因梅泉集之事之感。而献中国之说于吾故邦诸父兄。以为他日故邦之事有大于是集者。则以是集之所以成者为师。即中国之说也。虽然独止是哉。独止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