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x 页
李海鹤遗书卷八(固城李沂伯曾著)
文录[六]○记
文录[六]○记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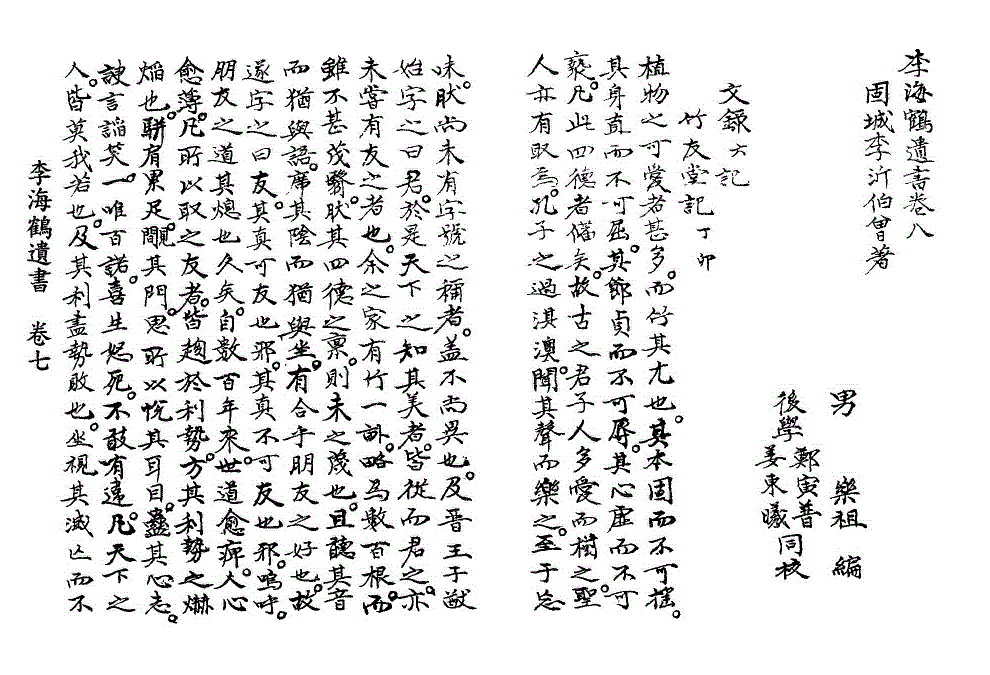 竹友堂记(丁卯)
竹友堂记(丁卯)植物之可爱者甚多。而竹其尤也。其本固而不可摇。其身直而不可屈。其节贞而不可辱。其心虚而不可亵。凡此四德者备矣。故古之君子人多爱而树之。圣人亦有取焉。孔子之过淇澳。闻其声而乐之。至于忘味。肰尚未有字号之称者。盖不尚异也。及晋王子猷始字之曰君。于是天下之知其美者。皆从而君之。亦未尝有友之者也。余之家有竹一亩。略为数百根。而虽不甚茂翳。肰其四德之禀。则未之蔑也。且听其音而犹与语。席其阴而犹与坐。有合乎朋友之好也。故遂字之曰友。其真可友也邪。其真不可友也邪。呜呼。朋友之道其熄也久矣。自数百年来。世道愈痹。人心愈薄。凡所以取之友者。皆趋于利势。方其利势之赫焰也。骈肩累足。覸其门。思所以悦其耳目。蛊其心志。谀言谄笑。一唯百诺。喜生怒死。不敢有违。凡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及其利尽势败也。坐视其灭亡而不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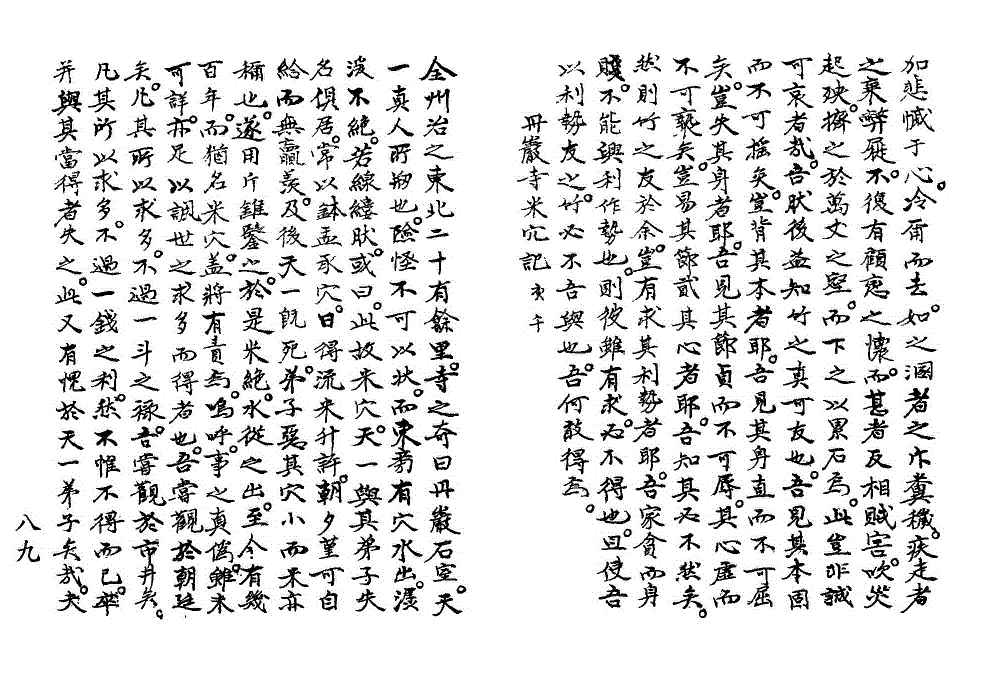 加悲戚于心。冷尔而去。如之溷者之斥粪秽。疾走者之弃弊屣。不复有顾恋之怀。而甚者反相贼害。吹灾起殃。挤之于万丈之壑。而下之以累石焉。此岂非诚可哀者哉。吾肰后益知竹之真可友也。吾见其本固而不可摇矣。岂背其本者耶。吾见其身直而不可屈矣。岂失其身者耶。吾见其节贞而不可辱。其心虚而不可亵矣。岂易其节贰其心者耶。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则竹之友于余。岂有求其利势者耶。吾家贫而身贱。不能兴利作势也。则彼虽有求。必不得也。且使吾以利势友之。竹必不吾与也。吾何敢得焉。
加悲戚于心。冷尔而去。如之溷者之斥粪秽。疾走者之弃弊屣。不复有顾恋之怀。而甚者反相贼害。吹灾起殃。挤之于万丈之壑。而下之以累石焉。此岂非诚可哀者哉。吾肰后益知竹之真可友也。吾见其本固而不可摇矣。岂背其本者耶。吾见其身直而不可屈矣。岂失其身者耶。吾见其节贞而不可辱。其心虚而不可亵矣。岂易其节贰其心者耶。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则竹之友于余。岂有求其利势者耶。吾家贫而身贱。不能兴利作势也。则彼虽有求。必不得也。且使吾以利势友之。竹必不吾与也。吾何敢得焉。丹岩寺米穴记(庚午)
全州治之东北二十有馀里。寺之奇曰丹岩石室。天一真人所刱也。险怪不可以状。而东旁有穴水出。潺湲不绝。若线缕肰。或曰。此故米穴。天一与其弟子失名俱居。常以钵盂承穴。日得流米升许。朝夕堇可自给而无赢羡。及后天一既死。弟子恶其穴小而米亦称也。遂用斤锥凿之。于是米绝。水从之出。至今有几百年。而犹名米穴。盖将有责焉。呜呼。事之真伪。虽未可详。亦足以讽世之求多而得者也。吾尝观于朝廷矣。凡其所以求多。不过一斗之禄。吾尝观于市井矣。凡其所以求多。不过一钱之利。然不惟不得而已。卒并与其当得者失之。此又有愧于天一弟子矣哉。夫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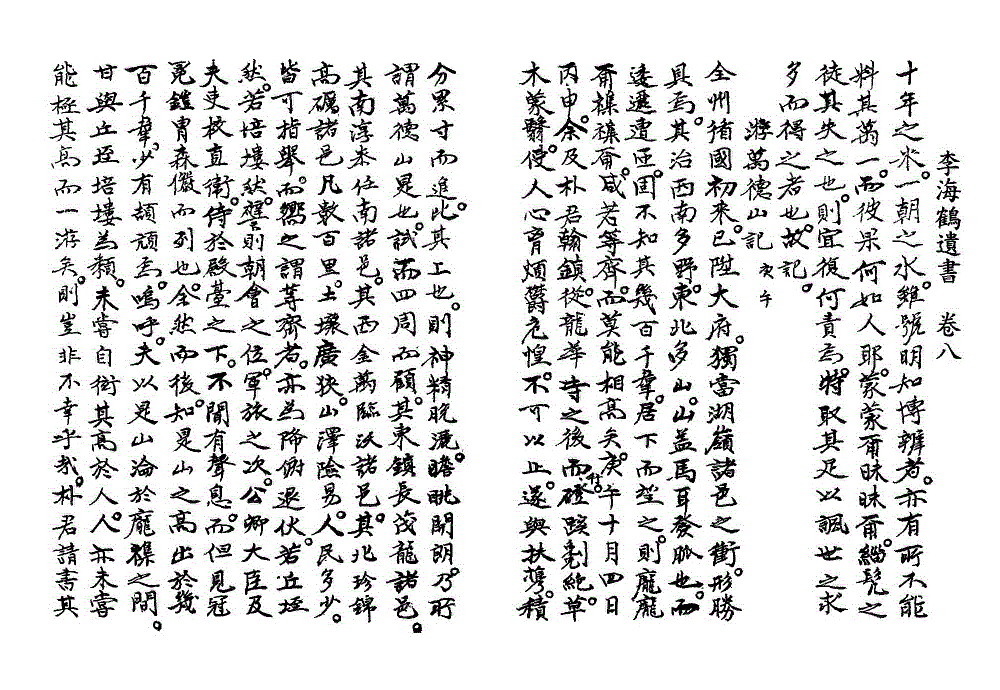 十年之米。一朝之水。虽号明知博辨者。亦有所不能料其万一。而彼果何如人耶。蒙蒙尔昧昧尔。缁髡之徒其失之也。则宜复何责焉。特取其足以讽世之求多而得之者也。故记。
十年之米。一朝之水。虽号明知博辨者。亦有所不能料其万一。而彼果何如人耶。蒙蒙尔昧昧尔。缁髡之徒其失之也。则宜复何责焉。特取其足以讽世之求多而得之者也。故记。游万德山记(庚午)
全州循国初来。已升大府。独当湖岭诸邑之冲。形胜具焉。其治西南多野。东北多山。山盖马耳发脉也。而逶逦遭匝。固不知其几百千群。居下而望之。则庞庞尔杂杂尔。咸若等齐。而莫能相高矣。庚午十月四日丙申。余及朴君翰镇。从龙华寺之后而行。磴蹊劖绝。草木蒙翳。使人心胸烦郁危惶。不可以止。遂与扶携。积分累寸而进。比其上也。则神精脱洒。瞻眺开朗。乃所谓万德山是也。试而四周而顾。其东镇长茂龙诸邑。其南淳泰任南诸邑。其西金万临沃诸邑。其北珍锦高砺诸邑凡数百里。土壤广狭。山泽险易。人民多少。皆可指举。而向之谓等齐者。亦为降俯退伏。若丘垤然。若培塿然。譬则朝会之位。军旅之次。公卿大臣及夫吏校直卫。侍于殿台之下。不闻有声息。而但见冠冕铠冑森俨而列也。余然而后。知是山之高出于几百千群。少有颉颃焉。呜呼。夫以是山沦于庞杂之间。甘与丘垤培塿为类。未尝自衒其高于人。人亦未尝能极其高而一游矣。则岂非不幸乎哉。朴君请书其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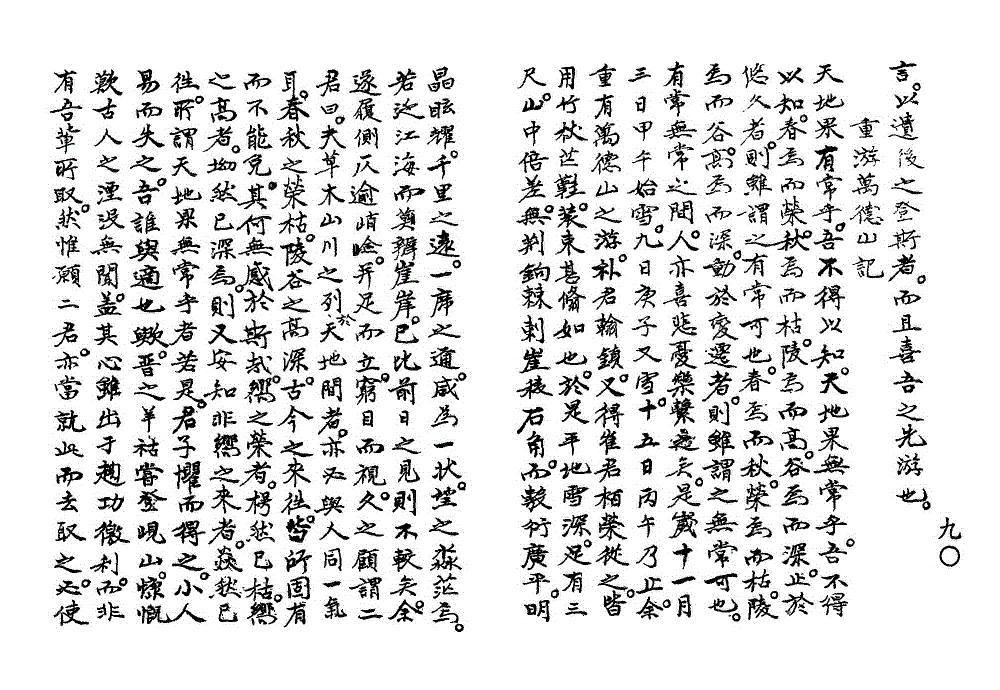 言。以遗后之登斯者。而且喜吾之先游也。
言。以遗后之登斯者。而且喜吾之先游也。重游万德山记
天地果有常乎。吾不得以知。天地果无常乎。吾不得以知。春焉而荣。秋焉而枯。陵焉而高。谷焉而深。止于悠久者。则虽谓之有常可也。春焉而秋。荣焉而枯。陵焉而谷。高焉而深。动于变迁者。则虽谓之无常可也。有常无常之间。人亦喜悲忧乐系之矣。是岁十一月三日甲午始雪。九日庚子又雪。十五日丙午乃止。余重有万德山之游。朴君翰镇。又得崔君柏荣从之。皆用竹杖芒鞋。装束甚翛如也。于是平地雪深。足有三尺。山中倍差。无荆钩棘刺崖棱石角。而敷衍广平。明晶眩耀。千里之远。一席之迩。咸为一状。望之淼茫焉。若泛江海而莫辨崖岸。已比前日之见则不较矣。余遂履侧仄逾峭崄。并足而立。穷目而视。久之顾谓二君曰。夫草木山川之列于天地间者。亦必与人同一气耳。春秋之荣枯。陵谷之高深。古今之来往。皆所固有而不能免。其何无感于斯哉。向之荣者。枵然已枯。向之高者。坳然已深焉。则又安知非向之来者。焱然已往。所谓天地果无常乎者若是。君子惧而得之。小人易而失之。吾谁与适也欤。晋之羊祜尝登岘山。慷慨叹古人之湮没无闻。盖其心虽出于趋功徼利。而非有吾辈所取。然惟愿二君。亦当就此而去取之。必使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1H 页
 道义文章。上轧有元。下驰无穷。以求免乎千百世之羊祜复叹此山幸矣。既已日降崦嵫。风兴涧壑。黯澹之色。清泠之气。令人神凄骨冷。不可留也。反宿龙华之寺。
道义文章。上轧有元。下驰无穷。以求免乎千百世之羊祜复叹此山幸矣。既已日降崦嵫。风兴涧壑。黯澹之色。清泠之气。令人神凄骨冷。不可留也。反宿龙华之寺。山水亭记(丙申)
士大夫进退用藏。其道不一。然而善进者常处于退。善用者常处于藏。夫人之所力争而造物所靳惜。莫甚乎名利。故求不以其时。获不以其义。而能免者。盖无几矣。则家居城市而存云林之思。身在绮纨而尚布素之志。此古哲人智士所以保功名全性命之术也。崔主事相宜甫。尝为余言其先君子少负才望。倜傥多奇节。年至三十而中进士。既已归乡里。搆屋于华岳之阴。曰山水亭。计将老焉。而不幸早世。今相宜不肖。不能追先君子之意。而来役于幕府。猜嫌生于前。谤议随于后。自顾所遇。懔然内恐。不若弃官南下。栖息山水之间。以乐其有。则一丘一壑。皆吾家物也。一泉一石。亦吾家物也。而乃舍此而趋彼。乞于不与。望于不施。则其为人之贤愚。果何如哉。呜呼。相宜甫其可谓知进退用藏之道者也。余虽不敏。而为世所识。游于卿士间久矣。今相宜甫年壮志盛。才礼而器备。又遭国家多事。急于求人之日。宜其手抵足投。以决死生于形势之途。而乃自恬然收止。熟视而不入。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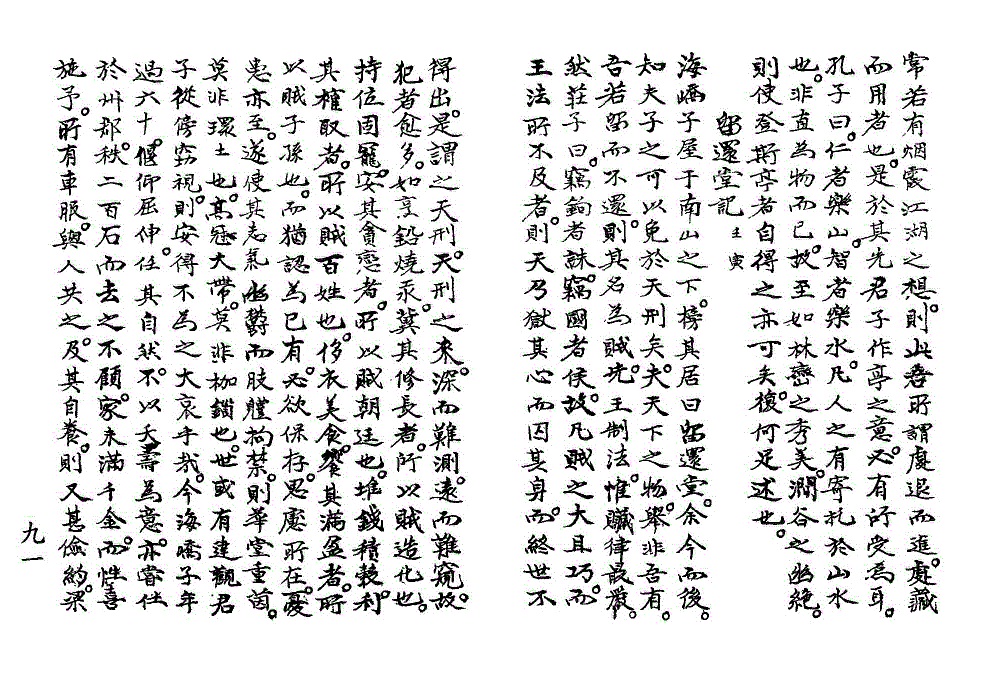 常若有烟霞江湖之想。则此吾所谓处退而进。处藏而用者也。是于其先君子作亭之意。必有所受为耳。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凡人之有寄托于山水也。非直为物而已。故至如林峦之秀美。涧谷之幽绝。则使登斯亭者自得之亦可矣。复何足述也。
常若有烟霞江湖之想。则此吾所谓处退而进。处藏而用者也。是于其先君子作亭之意。必有所受为耳。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凡人之有寄托于山水也。非直为物而已。故至如林峦之秀美。涧谷之幽绝。则使登斯亭者自得之亦可矣。复何足述也。留还堂记(壬寅)
海峤子屋于南山之下。榜其居曰留还堂。余今而后。知夫子之可以免于天刑矣。夫天下之物。举非吾有。吾若留而不还。则其名为贼。先王制法。惟赃律最严。然庄子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故凡贼之大且巧。而王法所不及者。则天乃狱其心而囚其身。而终世不得出。是谓之天刑。天刑之来。深而难测。远而难窥。故犯者愈多。如烹铅烧汞。冀其修长者。所以贼造化也。持位固宠。安其贪恋者。所以贼朝廷也。堆钱积谷。利其榷取者。所以贼百姓也。侈衣美食。飨其满盈者。所以贼子孙也。而犹认为己有。必欲保存。思虑所在。忧患亦至。遂使其志气幽郁而肢体拘禁。则华堂重茵。莫非环土也。高冠大带。莫非枷锁也。世或有达观君子从傍窃视。则安得不为之大哀乎哉。今海峤子年过六十。偃仰屈伸。任其自然。不以夭寿为意。亦尝仕于州郡。秩二百石而去之不顾。家未满千金。而性喜施予。所有车服。与人共之。及其自养。则又甚俭约。梁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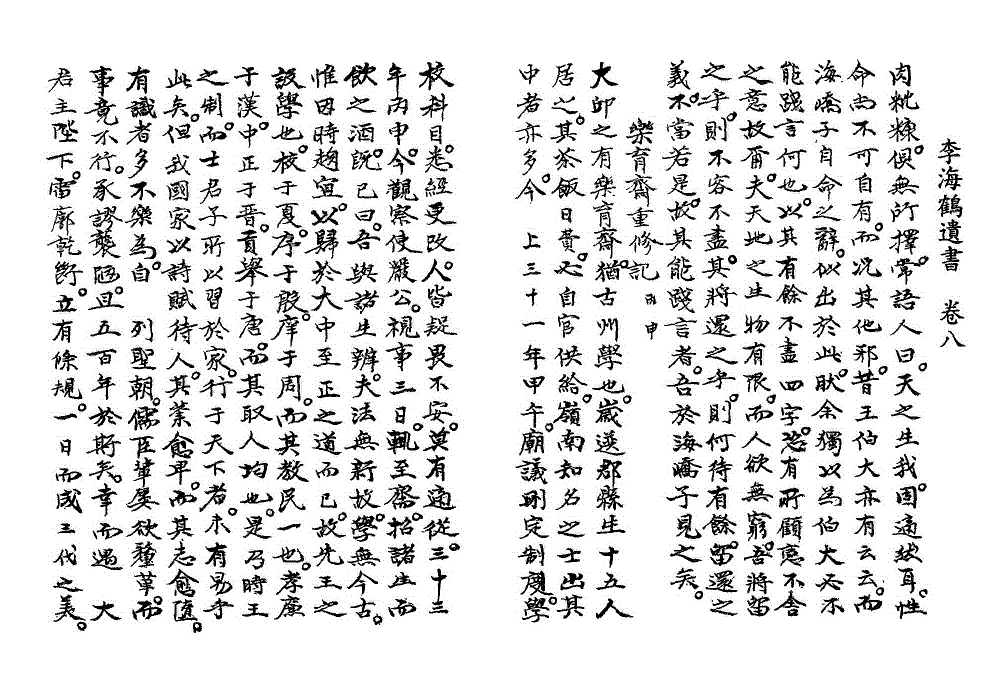 肉秕糠。俱无所择。常语人曰。天之生我。固适然耳。性命尚不可自有。而况其他邪。昔王伯大亦有云云。而海峤子自命之辞。似出于此。肰余独以为伯大必不能践言何也。以其有馀不尽四字。恐有所顾恋不舍之意故尔。夫天地之生物有限。而人欲无穷。吾将留之乎。则不容不尽。其将还之乎。则何待有馀。留还之义。不当若是。故其能践言者。吾于海峤子见之矣。
肉秕糠。俱无所择。常语人曰。天之生我。固适然耳。性命尚不可自有。而况其他邪。昔王伯大亦有云云。而海峤子自命之辞。似出于此。肰余独以为伯大必不能践言何也。以其有馀不尽四字。恐有所顾恋不舍之意故尔。夫天地之生物有限。而人欲无穷。吾将留之乎。则不容不尽。其将还之乎。则何待有馀。留还之义。不当若是。故其能践言者。吾于海峤子见之矣。乐育斋重修记(丙申)
大邱之有乐育斋。犹古州学也。岁选郡县生十五人居之。其茶饭日费。必自官供给。岭南知名之士出其中者亦多。今 上三十一年甲午。庙议删定制度。学校科目。悉经更改。人皆疑畏不安。莫有适从。三十三年丙申。今观察使严公。视事三日。辄至斋。招诸生而饮之酒。既已曰。吾与诸生辨。夫法无新故。学无今古。惟因时趋宜。以归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已。故先王之设学也。校于夏。序于殷。庠于周。而其教民一也。孝廉于汉。中正于晋。贡举于唐。而其取人均也。是乃时王之制。而士君子所以习于家。行于天下者。未有易乎此矣。但我国家以诗赋待人。其业愈卑。而其志愈堕。有识者多不乐为。自 列圣朝。儒臣辈屡欲釐革。而事竟不行。承谬袭陋。且五百年于斯矣。幸而遇 大君主陛下。雷廓乾断。立有条规。一日而成三代之美。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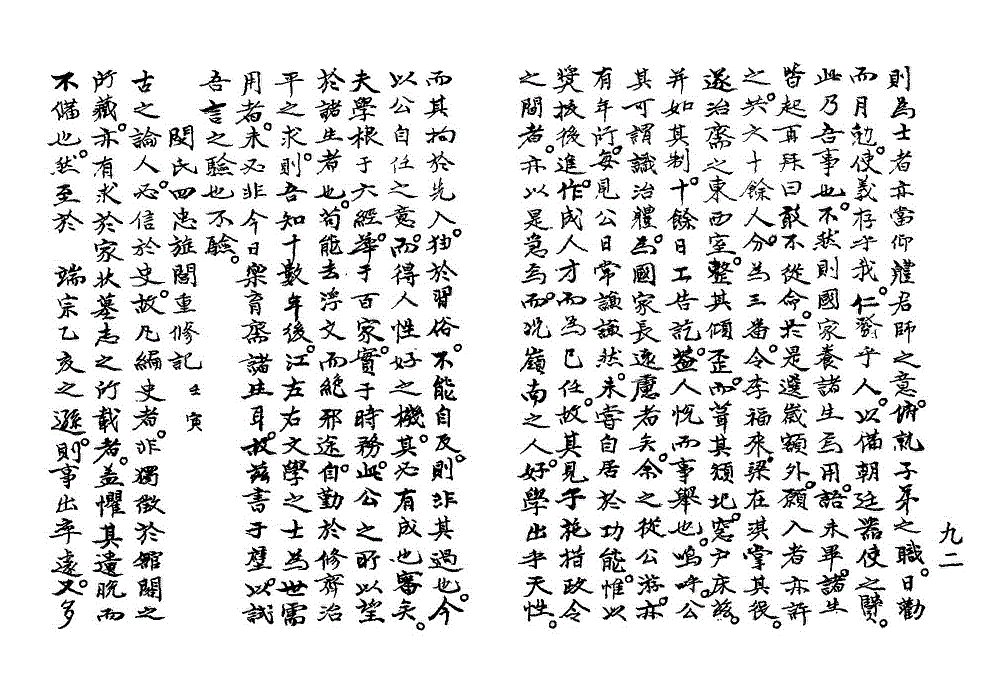 则为士者亦当仰体君师之意。俯就子弟之职。日劝而月勉。使义存乎我。仁发乎人。以备朝廷器使之贤。此乃吾事也。不然则国家养诸生焉用。语未毕。诸生皆起再拜曰敢不从命。于是选岁额外。愿入者亦许之。共六十馀人。分为三番。令李福来,梁在淇掌其役。遂治斋之东西室。整其倾歪。而葺其颓圮。窗户床玆。并如其制。十馀日工告讫。盖人悦而事举也。呜呼。公其可谓识治体。为国家长远虑者矣。余之从公游。亦有年所。每见公日常谦谦然。未尝自居于功能。惟以奖拔后进。作成人才而为己任。故其见于施措政令之间者。亦以是急焉。而况岭南之人。好学出乎天性。而其拘于先入。狃于习俗。不能自反。则非其过也。今以公自任之意。而得人性好之机。其必有成也审矣。夫学根于六经。华于百家。实于时务。此公之所以望于诸生者也。苟能去浮文而绝邪途。自勤于修齐治平之求。则吾知十数年后。江左右文学之士为世需用者。未必非今日乐育斋诸生耳。故玆书于壁。以试吾言之验也不验。
则为士者亦当仰体君师之意。俯就子弟之职。日劝而月勉。使义存乎我。仁发乎人。以备朝廷器使之贤。此乃吾事也。不然则国家养诸生焉用。语未毕。诸生皆起再拜曰敢不从命。于是选岁额外。愿入者亦许之。共六十馀人。分为三番。令李福来,梁在淇掌其役。遂治斋之东西室。整其倾歪。而葺其颓圮。窗户床玆。并如其制。十馀日工告讫。盖人悦而事举也。呜呼。公其可谓识治体。为国家长远虑者矣。余之从公游。亦有年所。每见公日常谦谦然。未尝自居于功能。惟以奖拔后进。作成人才而为己任。故其见于施措政令之间者。亦以是急焉。而况岭南之人。好学出乎天性。而其拘于先入。狃于习俗。不能自反。则非其过也。今以公自任之意。而得人性好之机。其必有成也审矣。夫学根于六经。华于百家。实于时务。此公之所以望于诸生者也。苟能去浮文而绝邪途。自勤于修齐治平之求。则吾知十数年后。江左右文学之士为世需用者。未必非今日乐育斋诸生耳。故玆书于壁。以试吾言之验也不验。闵氏四忠旌闾重修记(壬寅)
古之论人。必信于史。故凡编史者。非独徵于馆阁之所藏。亦有求于家状墓志之所载者。盖惧其遗脱而不备也。然至于 端宗乙亥之逊。则事出卒遽。又多
李海鹤遗书卷八 第 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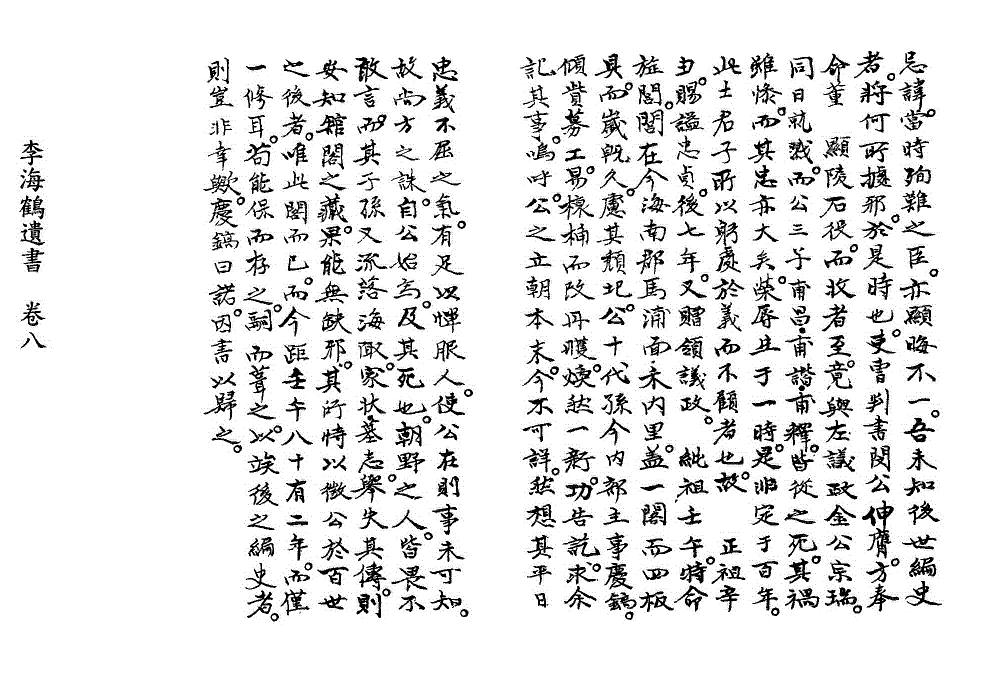 忌讳。当时殉难之臣。亦显晦不一。吾未知后世编史者。将何所据邪。于是时也。吏曹判书闵公伸膺。方奉命董 显陵石役。而收者至。竟与左议政金公宗瑞。同日就戮。而公三子甫昌,甫谐,甫释。皆从之死。其祸虽惨。而其忠亦大矣。荣辱生于一时。是非定于百年。此士君子所以躬处于义而不顾者也。故 正祖辛丑。赐谥忠贞。后七年。又赠领议政。 纯祖壬午。特命旌闾。闾在今海南郡马浦面禾内里。盖一阁而四板具。而岁既久。虑其颓圮。公十代孙今内部主事庆镐。倾赀募工。易榱桷而改丹雘。焕然一新。功告讫。求余记其事。呜呼。公之立朝本末。今不可详。然想其平日忠义不屈之气。有足以惮服人。使公在则事未可知。故尚方之诛。自公始焉。及其死也。朝野之人。皆畏不敢言。而其子孙又流落海陬。家状,墓志。举失其传。则安知馆阁之藏。果能无缺邪。其所恃以徵公于百世之后者。唯此阁而已。而今距壬午八十有二年。而仅一修耳。苟能保而存之。嗣而葺之。以俟后之编史者。则岂非幸欤。庆镐曰诺。因书以归之。
忌讳。当时殉难之臣。亦显晦不一。吾未知后世编史者。将何所据邪。于是时也。吏曹判书闵公伸膺。方奉命董 显陵石役。而收者至。竟与左议政金公宗瑞。同日就戮。而公三子甫昌,甫谐,甫释。皆从之死。其祸虽惨。而其忠亦大矣。荣辱生于一时。是非定于百年。此士君子所以躬处于义而不顾者也。故 正祖辛丑。赐谥忠贞。后七年。又赠领议政。 纯祖壬午。特命旌闾。闾在今海南郡马浦面禾内里。盖一阁而四板具。而岁既久。虑其颓圮。公十代孙今内部主事庆镐。倾赀募工。易榱桷而改丹雘。焕然一新。功告讫。求余记其事。呜呼。公之立朝本末。今不可详。然想其平日忠义不屈之气。有足以惮服人。使公在则事未可知。故尚方之诛。自公始焉。及其死也。朝野之人。皆畏不敢言。而其子孙又流落海陬。家状,墓志。举失其传。则安知馆阁之藏。果能无缺邪。其所恃以徵公于百世之后者。唯此阁而已。而今距壬午八十有二年。而仅一修耳。苟能保而存之。嗣而葺之。以俟后之编史者。则岂非幸欤。庆镐曰诺。因书以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