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书
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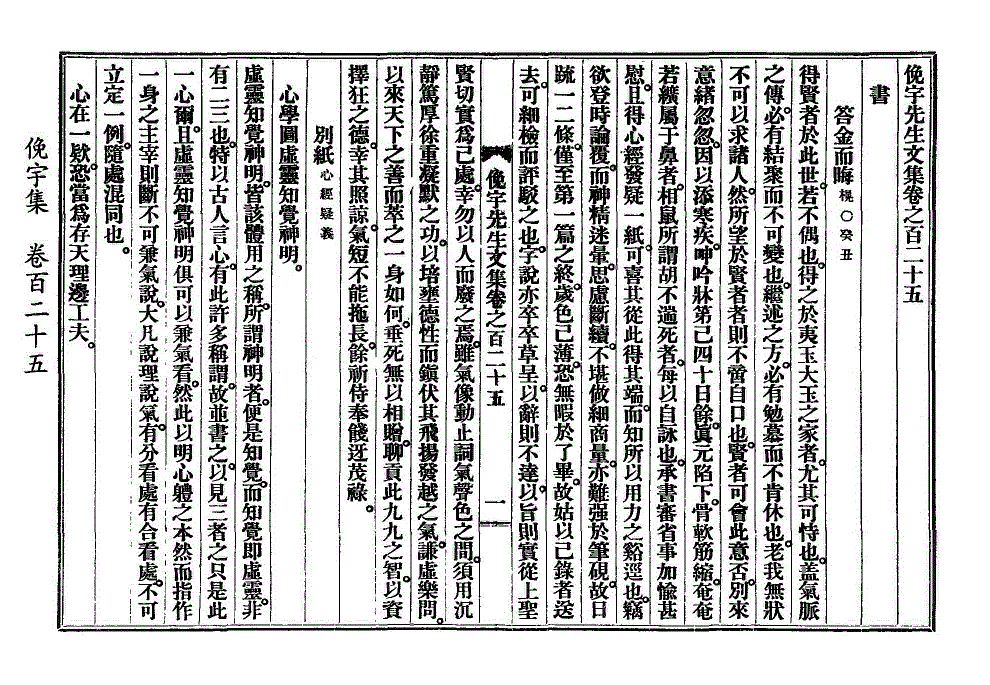 答金而晦(榥○癸丑)
答金而晦(榥○癸丑)得贤者于此世。若不偶也。得之于夷玉大玉之家者。尤其可恃也。盖气脉之传。必有结聚而不可变也。继述之方。必有勉慕而不肯休也。老我无状不可以求诸人。然所望于贤者者则不啻自口也。贤者可会此意否。别来意绪忽忽。因以添寒疾。呻吟床笫已四十日馀。真元陷下。骨软筋缩。奄奄若纩属于鼻者。相鼠所谓胡不遄死者。每以自咏也。承书审省事加愉甚慰。且得心经发疑一纸。可喜其从此得其端。而知所以用力之溪径也。窃欲登时论覆。而神精迷晕。思虑断续。不堪做细商量。亦难强于笔砚。故日疏一二条。仅至第一篇之终。岁色已薄。恐无暇于了毕。故姑以已录者送去。可细检而评驳之也。字说亦卒卒草呈。以辞则不达。以旨则实从上圣贤切实为己处。幸勿以人而废之焉。虽气像动止词气声色之间。须用沉静笃厚徐重凝默之功。以培壅德性而镇伏其飞扬发越之气。谦虚乐问。以来天下之善而萃之一身如何。垂死无以相赠。聊贡此九九之智。以资择狂之德。幸其照谅。气短不能拖长。馀祈侍奉饯迓茂禄。
别纸(心经疑义)
心学图虚灵知觉神明。
虚灵知觉神明。皆该体用之称。所谓神明者。便是知觉。而知觉即虚灵。非有二三也。特以古人言心。有此许多称谓。故并书之。以见三者之只是此一心尔。且虚灵知觉神明俱可以兼气看。然此以明心体之本然而指作一身之主宰则断不可兼气说。大凡说理说气。有分看处有合看处。不可立定一例。随处混同也。
心在一款。恐当为存天理边工夫。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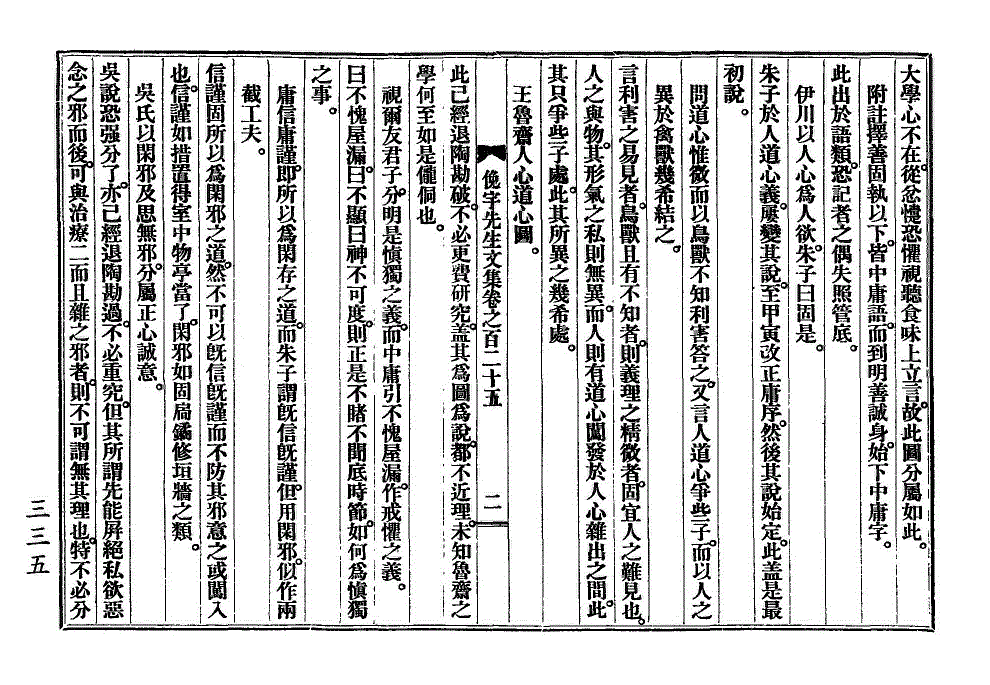 大学心不在。从忿懥恐惧视听食味上立言。故此图分属如此。
大学心不在。从忿懥恐惧视听食味上立言。故此图分属如此。附注择善固执以下。皆中庸语。而到明善诚身。始下中庸字。
此出于语类。恐记者之偶失照管底。
伊川以人心为人欲。朱子曰固是。
朱子于人道心义。屡变其说。至甲寅改正庸序。然后其说始定。此盖是最初说。
问道心惟微而以鸟兽不知利害答之。又言人道心争些子。而以人之异于禽兽几希结之。
言利害之易见者。鸟兽且有不知者。则义理之精微者。固宜人之难见也。人之与物。其形气之私则无异。而人则有道心闯发于人心杂出之间。此其只争些子处。此其所异之几希处。
王鲁斋人心道心图。
此已经退陶勘破。不必更费研究。盖其为图为说。都不近理。未知鲁斋之学何至如是儱侗也。
视尔友君子。分明是慎独之义。而中庸引不愧屋漏。作戒惧之义。
曰不愧屋漏。曰不显曰神不可度。则正是不睹不闻底时节。如何为慎独之事。
庸信庸谨。即所以为闲存之道。而朱子谓既信既谨。但用闲邪。似作两截工夫。
信谨固所以为闲邪之道。然不可以既信既谨而不防其邪意之或闯入也。信谨如措置得室中物亭当了。闲邪如固扃鐍修垣墙之类。
吴氏以闲邪及思无邪。分属正心诚意。
吴说恐强分了。亦已经退陶勘过。不必重究。但其所谓先能屏绝私欲恶念之邪而后。可与治疗二而且杂之邪者。则不可谓无其理也。特不必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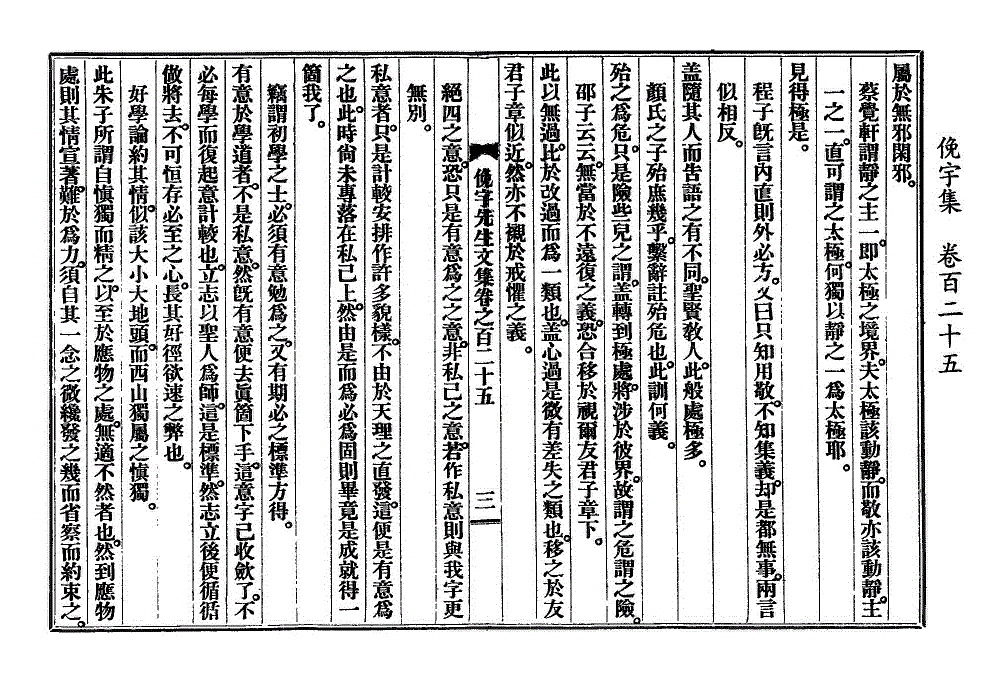 属于无邪闲邪。
属于无邪闲邪。蔡觉轩谓静之主一。即太极之境界。夫太极该动静。而敬亦该动静。主一之一。直可谓之太极。何独以静之一为太极耶。
见得极是。
程子既言内直则外必方。又曰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两言似相反。
盖随其人而告语之有不同。圣贤教人。此般处极多。
颜氏之子殆庶几乎。系辞注殆危也。此训何义。
殆之为危。只是险些儿之谓。盖转到极处。将涉于彼界。故谓之危谓之险。
邵子云云。无当于不远复之义。恐合移于视尔友君子章下。
此以无过。比于改过而为一类也。盖心过是微有差失之类也。移之于友君子章似近。然亦不衬于戒惧之义。
绝四之意。恐只是有意为之之意。非私己之意。若作私意则与我字更无别。
私意者。只是计较安排作许多貌样。不由于天理之直发。这便是有意为之也。此时尚未专落在私己上。然由是而为必为固则毕竟是成就得一个我了。
窃谓初学之士。必须有意勉为之。又有期必之标准方得。
有意于学道者。不是私意。然既有意便去真个下手。这意字已收敛了。不必每学而复起意计较也。立志以圣人为师。这是标准。然志立后便循循做将去。不可恒存必至之心。长其好径欲速之弊也。
好学论约其情。似该大小大地头。而西山独属之慎独。
此朱子所谓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适不然者也。然到应物处则其情宣著。难于为力。须自其一念之微才发之几而省察而约束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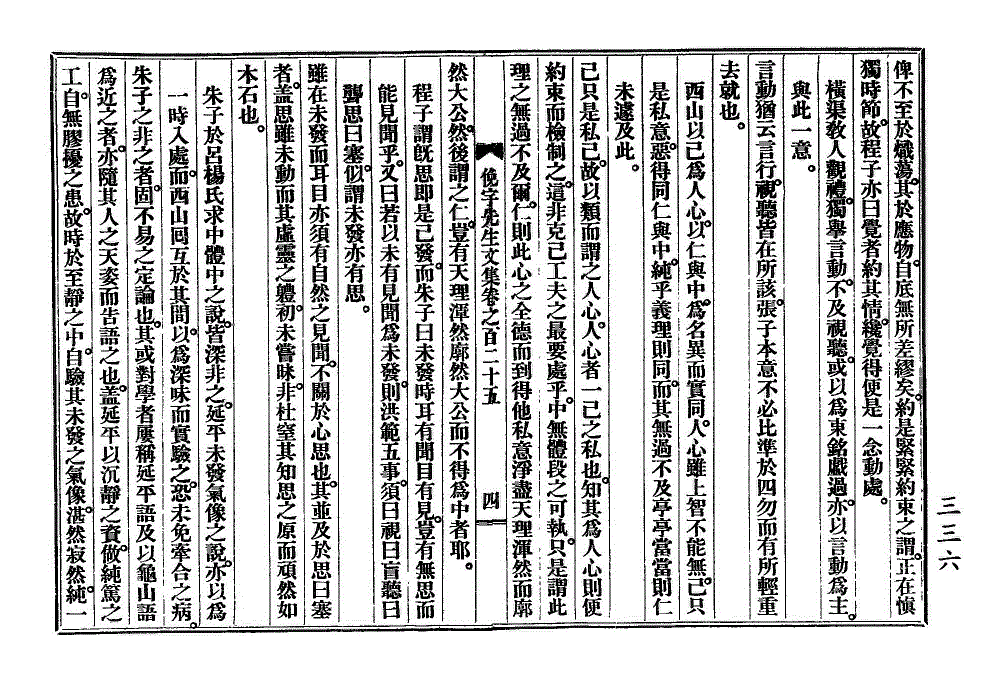 俾不至于炽荡。其于应物。自底无所差缪矣。约是紧紧约束之谓。正在慎独时节。故程子亦曰觉者约其情。才觉得便是一念动处。
俾不至于炽荡。其于应物。自底无所差缪矣。约是紧紧约束之谓。正在慎独时节。故程子亦曰觉者约其情。才觉得便是一念动处。横渠教人观礼。独举言动。不及视听。或以为东铭戏过。亦以言动为主。与此一意。
言动犹云言行。视听皆在所该。张子本意不必比准于四勿而有所轻重去就也。
西山以己为人心。以仁与中。为名异而实同。人心虽上智不能无。己只是私意。恶得同仁与中。纯乎义理则同。而其无过不及亭亭当当则仁未遽及此。
己只是私己。故以类而谓之人心。人心者一己之私也。知其为人心则便约束而检制之。这非克己工夫之最要处乎。中无体段之可执。只是谓此理之无过不及尔。仁则此心之全德而到得他私意净尽天理浑然而廓然大公。然后谓之仁。岂有天理浑然廓然大公而不得为中者耶。
程子谓既思即是已发。而朱子曰未发时耳有闻目有见。岂有无思而能见闻乎。又曰若以未有见闻为未发。则洪范五事。须曰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似谓未发亦有思。
虽在未发而耳目亦须有自然之见闻。不关于心思也。其并及于思曰塞者。盖思虽未动而其虚灵之体。初未尝昧。非杜窒其知思之原而顽然如木石也。
朱子于吕杨氏求中体中之说。皆深非之。延平未发气像之说。亦以为一时入处。而西山回互于其间。以为深味而实验之。恐未免牵合之病。
朱子之非之者。固不易之定论也。其或对学者屡称延平语及以龟山语为近之者。亦随其人之天姿而告语之也。盖延平以沉静之资。做纯笃之工。自无胶扰之患。故时于至静之中。自验其未发之气像。湛然寂然。纯一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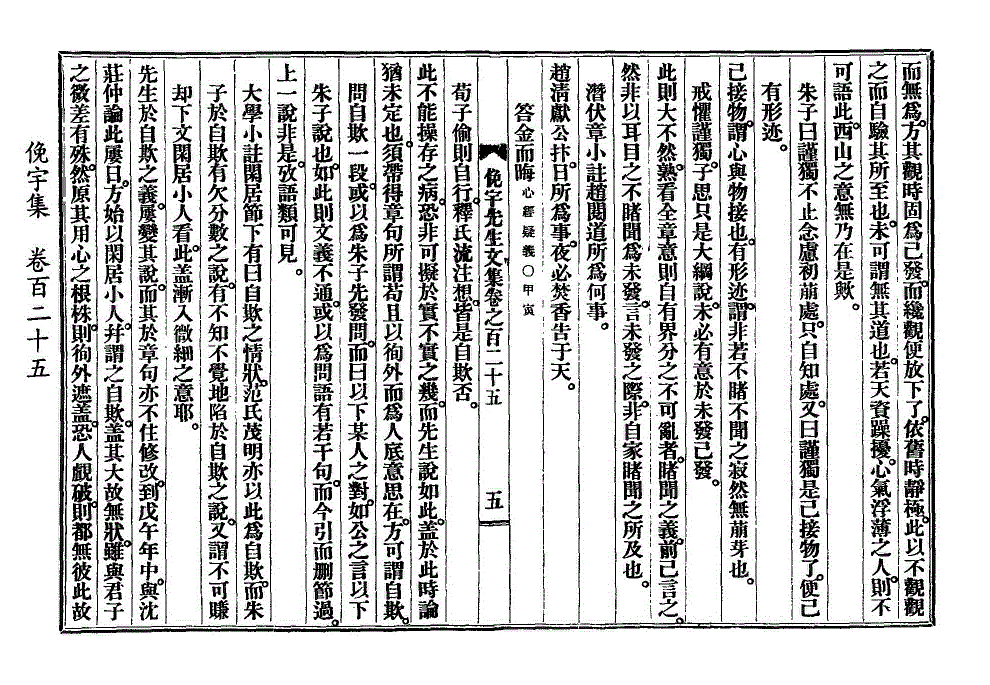 而无为。方其观时固为已发。而才观便放下了。依旧时静极。此以不观观之而自验其所至也。未可谓无其道也。若天资躁扰。心气浮薄之人。则不可语此。西山之意无乃在是欤。
而无为。方其观时固为已发。而才观便放下了。依旧时静极。此以不观观之而自验其所至也。未可谓无其道也。若天资躁扰。心气浮薄之人。则不可语此。西山之意无乃在是欤。朱子曰谨独不止念虑初萌处。只自知处。又曰谨独是已接物了。便已有形迹。
已接物。谓心与物接也。有形迹。谓非若不睹不闻之寂然无萌芽也。
戒惧谨独。子思只是大纲说。未必有意于未发已发。
此则大不然。熟看全章意则自有界分之不可乱者。睹闻之义。前已言之。然非以耳目之不睹闻为未发。言未发之际。非自家睹闻之所及也。
潜伏章小注赵阅道所为何事。
赵清献公抃。日所为事。夜必焚香告于天。
答金而晦(心经疑义○甲寅)
荀子偷则自行。释氏流注想。皆是自欺否。
此不能操存之病。恐非可拟于实不实之几。而先生说如此。盖于此时论犹未定也。须带得章句所谓苟且以徇外而为人底意思在。方可谓自欺。
问自欺一段。或以为朱子先发问。而曰以下某人之对。如公之言以下朱子说也。如此则文义不通。或以为问语有若干句。而今引而删节过。
上一说非是。考语类可见。
大学小注闲居节下有曰自欺之情状。范氏茂明亦以此为自欺。而朱子于自欺有欠分数之说。有不知不觉地陷于自欺之说。又谓不可赚却下文闲居小人看。此盖渐入微细之意耶。
先生于自欺之义。屡变其说。而其于章句亦不住修改。到戊午年中。与沈庄仲论此屡日。方始以闲居小人。并谓之自欺。盖其大故无状。虽与君子之微差有殊。然原其用心之根株。则徇外遮盖。恐人觑破。则都无彼此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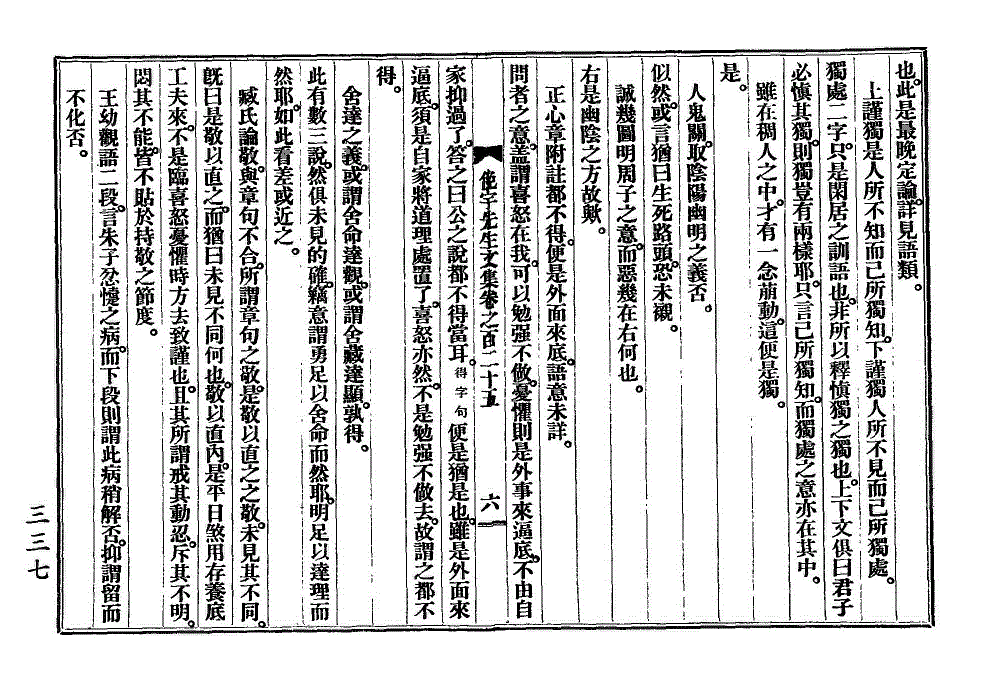 也。此是最晚定论。详见语类。
也。此是最晚定论。详见语类。上谨独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下谨独人所不见而己所独处。
独处二字。只是闲居之训语也。非所以释慎独之独也。上下文俱曰君子必慎其独。则独岂有两样耶。只言己所独知。而独处之意亦在其中。
虽在稠人之中。才有一念萌动。这便是独。
是。
人鬼关。取阴阳幽明之义否。
似然。或言犹曰生死路头。恐未衬。
诚几图明周子之意。而恶几在右何也。
右是幽阴之方故欤。
正心章附注都不得。便是外面来底。语意未详。
问者之意。盖谓喜怒在我。可以勉强不做。忧惧则是外事来逼底。不由自家抑过了。答之曰公之说都不得当耳。(得字句)便是犹是也。虽是外面来逼底。须是自家将道理处置了。喜怒亦然。不是勉强不做去。故谓之都不得。
舍达之义。或谓舍命达观。或谓舍藏达显。孰得。
此有数三说。然俱未见的确。窃意谓勇足以舍命而然耶。明足以达理而然耶。如此看差或近之。
臧氏论敬。与章句不合。所谓章句之敬。是敬以直之之敬。未见其不同。
既曰是敬以直之。而犹曰未见不同何也。敬以直内。是平日煞用存养底工夫来。不是临喜怒忧惧时方去致谨也。且其所谓戒其动忍。斥其不明。闷其不能。皆不贴于持敬之节度。
王幼观语二段。言朱子忿懥之病。而下段则谓此病稍解否。抑谓留而不化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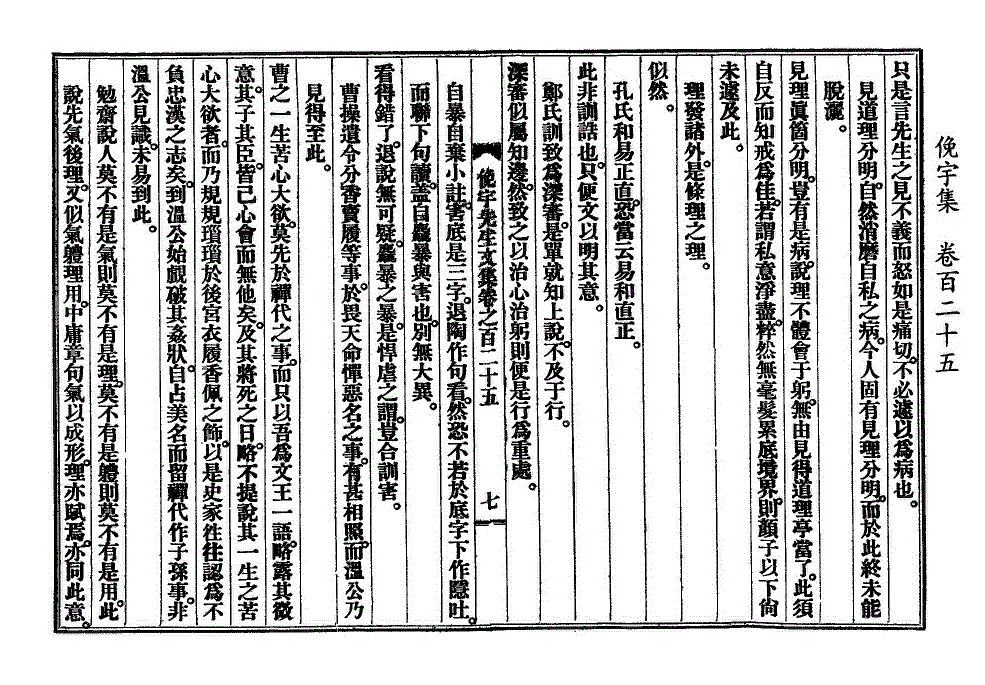 只是言先生之见不义而怒如是痛切。不必遽以为病也。
只是言先生之见不义而怒如是痛切。不必遽以为病也。见道理分明。自然消磨自私之病。今人固有见理分明。而于此终未能脱洒。
见理真个分明。岂有是病。说理不体会于躬。无由见得道理亭当了。此须自反而知戒为佳。若谓私意净尽。粹然无毫发累底境界。则颜子以下尚未遽及此。
理发诸外。是条理之理。
似然。
孔氏和易正直。恐当云易和直正。
此非训诰也。只便文以明其意。
郑氏训致为深审。是单就知上说。不及于行。
深审似属知边。然致之以治心治躬则便是行为重处。
自暴自弃小注。害底是三字。退陶作句看。然恐不若于底字下作隐吐。而联下句读。盖自粗暴与害也。别无大异。
看得错了。退说无可疑。粗暴之暴。是悍虐之谓。岂合训害。
曹操遗令分香卖履等事。于畏天命惮恶名之事。有甚相照。而温公乃见得至此。
曹之一生苦心大欲。莫先于禅代之事。而只以吾为文王一语。略露其微意。其子其臣。皆已心会而无他矣。及其将死之日。略不提说其一生之苦心大欲者。而乃规规琐琐于后宫衣履香佩之饰。以是史家往往认为不负忠汉之志矣。到温公始觑破其奸状。自占美名而留禅代作子孙事。非温公见识。未易到此。
勉斋说人莫不有是气则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体则莫不有是用。此说先气后理。又似气体理用。中庸章句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亦同此意。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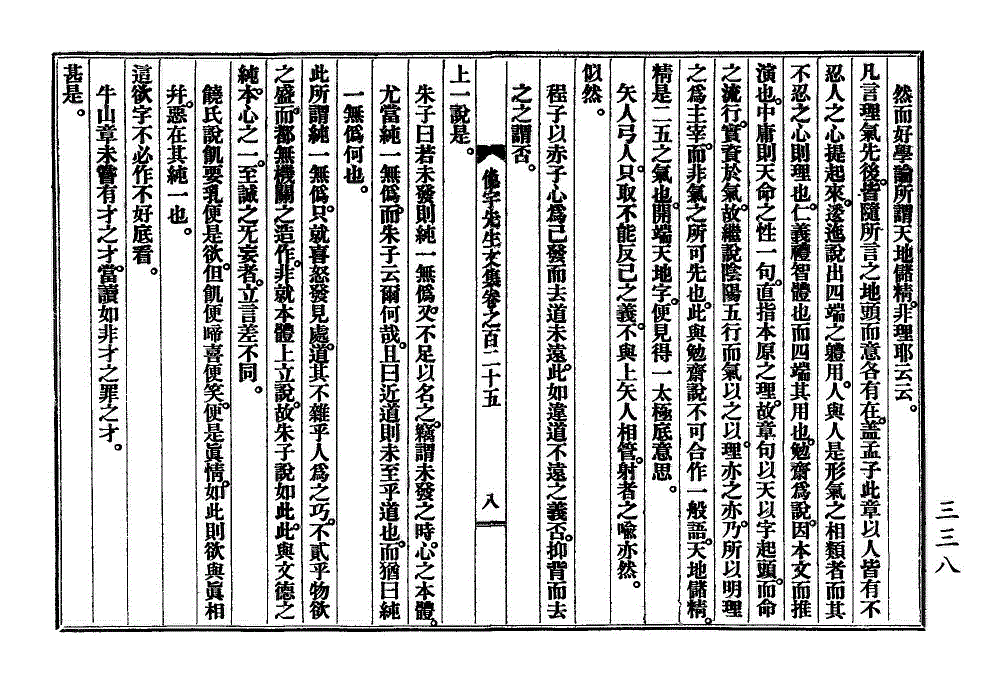 然而好学论所谓天地储精。非理耶云云。
然而好学论所谓天地储精。非理耶云云。凡言理气先后。皆随所言之地头而意各有在。盖孟子此章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提起来。逶迤说出四端之体用。人与人是形气之相类者而其不忍之心则理也。仁义礼智体也而四端其用也。勉斋为说。因本文而推演也。中庸则天命之性一句。直指本原之理。故章句以天以字起头。而命之流行。实资于气。故继说阴阳五行而气以之以。理亦之亦。乃所以明理之为主宰。而非气之所可先也。此与勉斋说不可合作一般语。天地储精。精是二五之气也。开端天地字。便见得一太极底意思。
矢人弓人。只取不能反己之义。不与上矢人相管。射者之喻亦然。
似然。
程子以赤子心为已发而去道未远。此如违道不远之义否。抑背而去之之谓否。
上一说是。
朱子曰若未发则纯一无伪。又不足以名之。窃谓未发之时。心之本体。尤当纯一无伪。而朱子云尔何哉。且曰近道则未至乎道也。而犹曰纯一无伪何也。
此所谓纯一无伪。只就喜怒发见处。道其不杂乎人为之巧。不贰乎物欲之盛。而都无机关之造作。非就本体上立说。故朱子说如此。此与文德之纯。本心之一。至诚之无妄者。立言差不同。
饶氏说饥要乳便是欲。但饥便啼喜便笑。便是真情。如此则欲与真相并。恶在其纯一也。
这欲字不必作不好底看。
牛山章未尝有才之才。当读如非才之罪之才。
甚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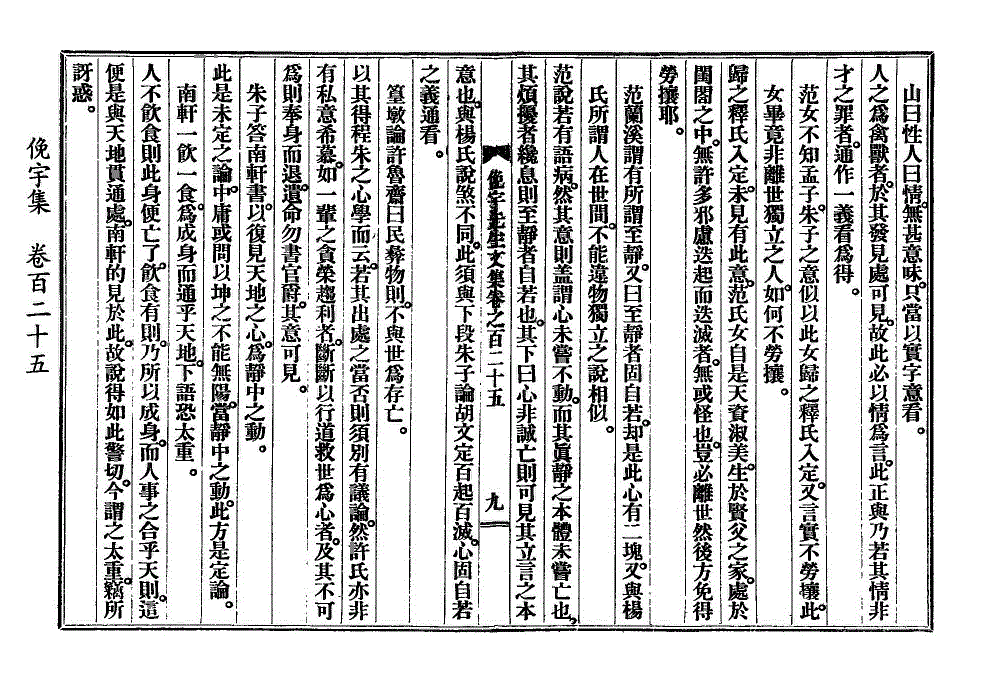 山曰性人曰情。无甚意味。只当以实字意看。
山曰性人曰情。无甚意味。只当以实字意看。人之为禽兽者。于其发见处可见。故此必以情为言。此正与乃若其情非才之罪者。通作一义看为得。
范女不知孟子。朱子之意似以此女归之释氏入定。又言实不劳攘。此女毕竟非离世独立之人。如何不劳攘。
归之释氏入定。未见有此意。范氏女自是天资淑美。生于贤父之家。处于闺閤之中。无许多邪虑迭起而迭灭者。无或怪也。岂必离世然后方免得劳攘耶。
范兰溪谓有所谓至静。又曰至静者固自若。却是此心有二块。又与杨氏所谓人在世间。不能违物独立之说相似。
范说若有语病。然其意则盖谓心未尝不动。而其真静之本体未尝亡也。其烦扰者才息则至静者自若也。其下曰心非诚亡则可见其立言之本意也。与杨氏说煞不同。此须与下段朱子论胡文定百起百灭。心固自若之义通看。
篁墩论许鲁斋曰民彝物则。不与世为存亡。
以其得程朱之心学而云。若其出处之当否则须别有议论。然许氏亦非有私意希慕。如一辈之贪荣趋利者。断断以行道救世为心者。及其不可为则奉身而退。遗命勿书官爵。其意可见。
朱子答南轩书。以复见天地之心。为静中之动。
此是未定之论。中庸或问以坤之不能无阳。当静中之动。此方是定论。
南轩一饮一食。为成身而通乎天地。下语恐太重。
人不饮食则此身便亡了。饮食有则。乃所以成身。而人事之合乎天则。这便是与天地贯通处。南轩的见于此。故说得如此警切。今谓之太重。窃所讶惑。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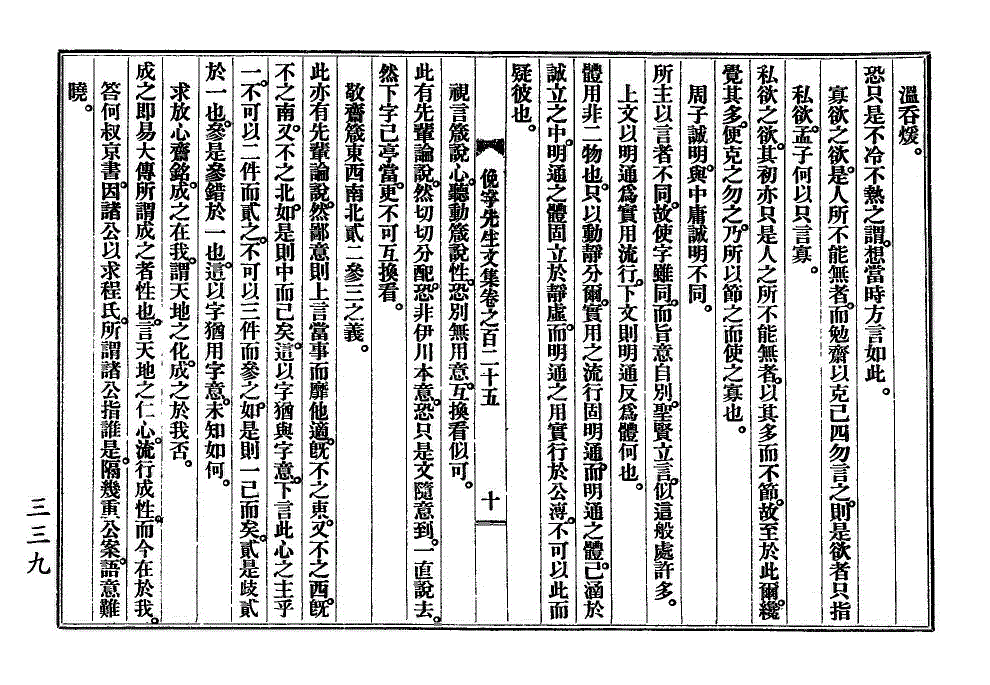 温吞煖。
温吞煖。恐只是不冷不热之谓。想当时方言如此。
寡欲之欲。是人所不能无者。而勉斋以克己四勿言之。则是欲者只指私欲。孟子何以只言寡。
私欲之欲。其初亦只是人之所不能无者。以其多而不节。故至于此尔。才觉其多。便克之勿之。乃所以节之而使之寡也。
周子诚明。与中庸诚明不同。
所主以言者不同。故使字虽同。而旨意自别。圣贤立言。似这般处许多。
上文以明通为实用流行。下文则明通反为体何也。
体用非二物也。只以动静分尔。实用之流行固明通。而明通之体。已涵于诚立之中。明通之体固立于静虚。而明通之用实行于公溥。不可以此而疑彼也。
视言箴说心。听动箴说性。恐别无用意。互换看似可。
此有先辈论说。然切切分配。恐非伊川本意。恐只是文随意到。一直说去。然下字已亭当。更不可互换看。
敬斋箴东西南北贰二参三之义。
此亦有先辈论说。然鄙意则上言当事而靡他适。既不之东。又不之西。既不之南。又不之北。如是则中而已矣。这以字犹与字意。下言此心之主乎一。不可以二件而贰之。不可以三件而参之。如是则一已而矣。贰是歧贰于一也。参是参错于一也。这以字犹用字意。未知如何。
求放心斋铭。成之在我。谓天地之化。成之于我否。
成之即易大传所谓成之者性也。言天地之仁心。流行成性。而今在于我。
答何叔京书。因诸公以求程氏。所谓诸公指谁是。隔几重公案。语意难晓。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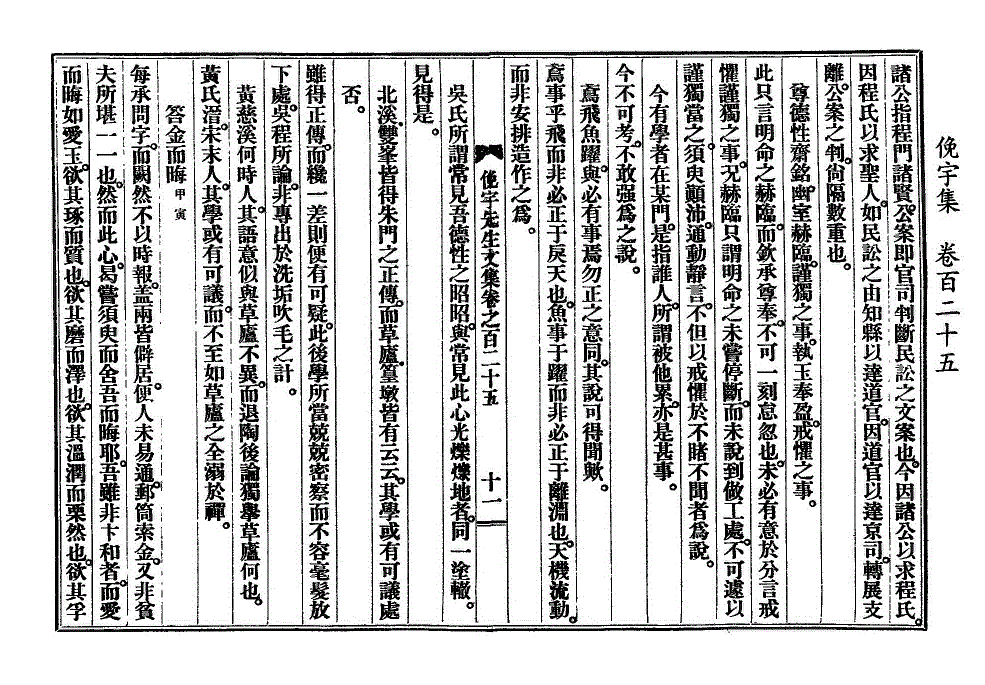 诸公指程门诸贤。公案即官司判断民讼之文案也。今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如民讼之由知县以达道官。因道官以达京司。转展支离。公案之判。尚隔数重也。
诸公指程门诸贤。公案即官司判断民讼之文案也。今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如民讼之由知县以达道官。因道官以达京司。转展支离。公案之判。尚隔数重也。尊德性斋铭。幽室赫临。谨独之事。执玉奉盈。戒惧之事。
此只言明命之赫临。而钦承尊奉。不可一刻怠忽也。未必有意于分言戒惧谨独之事。况赫临只谓明命之未尝停断。而未说到做工处。不可遽以谨独当之。须臾颠沛。通动静言。不但以戒惧于不睹不闻者为说。
今有学者在某门。是指谁人。所谓被他累。亦是甚事。
今不可考。不敢强为之说。
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其说可得闻欤。
鸢事乎飞而非必正于戾天也。鱼事于跃而非必正于离渊也。天机流动。而非安排造作之为。
吴氏所谓常见吾德性之昭昭。与常见此心光烁烁地者。同一涂辙。
见得是。
北溪,双峰皆得朱门之正传。而草庐,篁墩皆有云云。其学或有可议处否。
虽得正传。而才一差则便有可疑。此后学所当兢兢密察而不容毫发放下处。吴程所论。非专出于洗垢吹毛之计。
黄慈溪何时人。其语意似与草庐不异。而退陶后论独举草庐何也。
黄氏溍。宋末人。其学或有可议。而不至如草庐之全溺于禅。
答金而晦(甲寅)
每承问字。而阙然不以时报。盖两皆僻居。便人未易通。邮筒索金。又非贫夫所堪一一也。然而此心。曷尝须臾而舍吾而晦耶。吾虽非卞和者。而爱而晦如爱玉。欲其琢而质也。欲其磨而泽也。欲其温润而栗然也。欲其孚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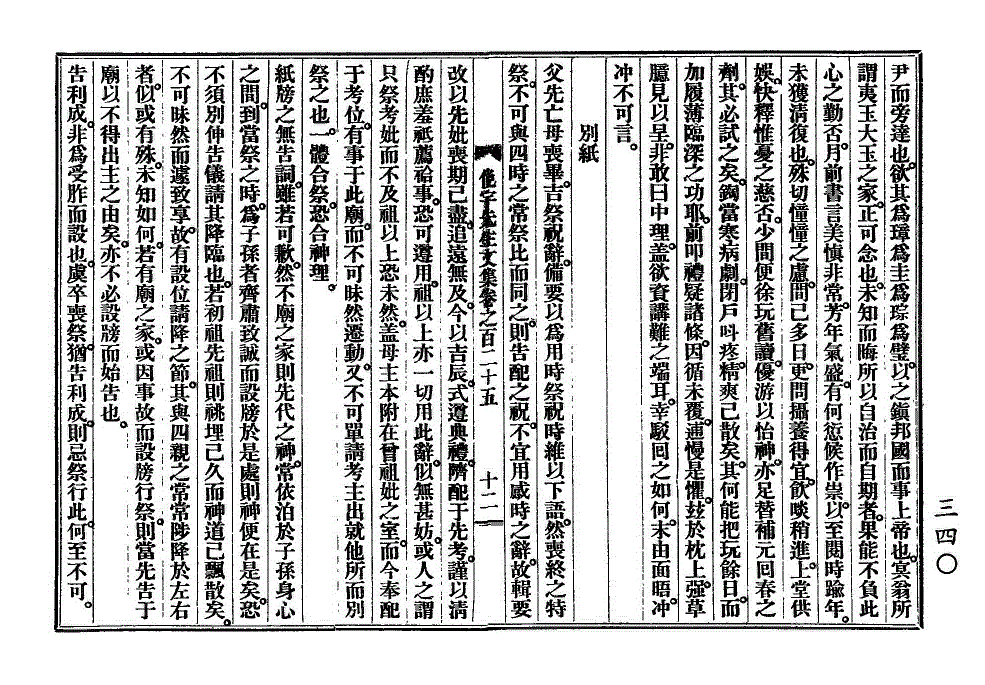 尹而旁达也。欲其为璋为圭为琮为璧。以之镇邦国而事上帝也。冥翁所谓夷玉大玉之家。正可念也。未知而晦所以自治而自期者。果能不负此心之勤否。月前书言美慎非常。芳年气盛。有何愆候作祟。以至阅时踰年。未获清复也。殊切憧憧之虑。间已多日。更问摄养得宜。饮啖稍进。上堂供娱。快释惟忧之慈否。少间便徐玩旧读。优游以怡神。亦足替补元回春之剂。其必试之矣。鋾当寒病剧。闭户叫疼。精爽已散矣。其何能把玩馀日。而加履薄临深之功耶。前叩礼疑诸条。因循未覆。逋慢是惧。玆于枕上。强草臆见以呈。非敢曰中理。盖欲资讲难之端耳。幸驳回之如何。末由面晤。冲冲不可言。
尹而旁达也。欲其为璋为圭为琮为璧。以之镇邦国而事上帝也。冥翁所谓夷玉大玉之家。正可念也。未知而晦所以自治而自期者。果能不负此心之勤否。月前书言美慎非常。芳年气盛。有何愆候作祟。以至阅时踰年。未获清复也。殊切憧憧之虑。间已多日。更问摄养得宜。饮啖稍进。上堂供娱。快释惟忧之慈否。少间便徐玩旧读。优游以怡神。亦足替补元回春之剂。其必试之矣。鋾当寒病剧。闭户叫疼。精爽已散矣。其何能把玩馀日。而加履薄临深之功耶。前叩礼疑诸条。因循未覆。逋慢是惧。玆于枕上。强草臆见以呈。非敢曰中理。盖欲资讲难之端耳。幸驳回之如何。末由面晤。冲冲不可言。别纸
父先亡母丧毕。吉祭祝辞。备要以为用时祭祝时维以下语。然丧终之特祭。不可与四时之常祭比而同之。则告配之祝。不宜用感时之辞。故辑要改以先妣丧期已尽。追远无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礼。隮配于先考。谨以清酌庶羞祗荐祫事。恐可遵用。祖以上亦一切用此辞。似无甚妨。或人之谓只祭考妣而不及祖以上恐未然。盖母主本附在曾祖妣之室。而今奉配于考位。有事于此庙。而不可昧然迁动。又不可单请考主出就他所而别祭之也。一体合祭。恐合神理。
纸榜之无告词。虽若可歉。然不庙之家则先代之神。常依泊于子孙身心之间。到当祭之时。为子孙者齐肃致诚而设榜于是处则神便在是矣。恐不须别伸告仪请其降临也。若初祖先祖则祧埋已久而神道已飘散矣。不可昧然而遽致享。故有设位请降之节。其与四亲之常常陟降于左右者。似或有殊。未知如何。若有庙之家。或因事故而设榜行祭。则当先告于庙以不得出主之由矣。亦不必设榜而始告也。
告利成。非为受胙而设也。虞卒丧祭。犹告利成。则忌祭行此。何至不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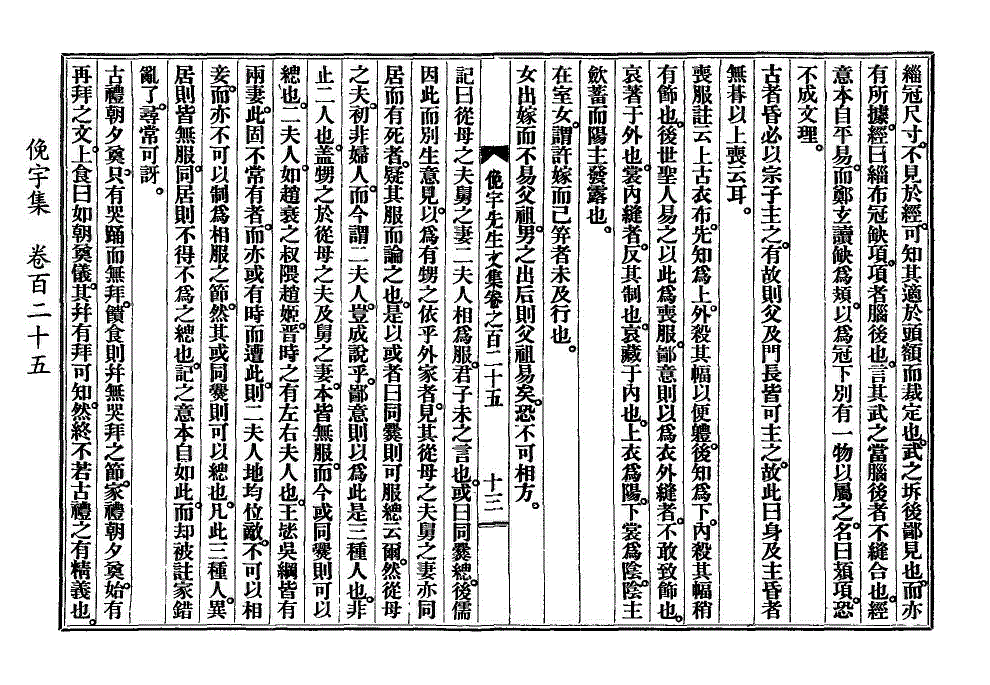 缁冠尺寸。不见于经。可知其适于头额而裁定也。武之坼后鄙见也。而亦有所据。经曰缁布冠缺项。项者脑后也。言其武之当脑后者不缝合也。经意本自平易。而郑玄读缺为頍。以为冠下别有一物以属之。名曰頍项。恐不成文理。
缁冠尺寸。不见于经。可知其适于头额而裁定也。武之坼后鄙见也。而亦有所据。经曰缁布冠缺项。项者脑后也。言其武之当脑后者不缝合也。经意本自平易。而郑玄读缺为頍。以为冠下别有一物以属之。名曰頍项。恐不成文理。古者昏必以宗子主之。有故则父及门长皆可主之。故此曰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云耳。
丧服注云上古衣布。先知为上。外杀其幅以便体。后知为下。内杀其幅稍有饰也。后世圣人易之以此为丧服。鄙意则以为衣外缝者。不敢致饰也。哀著于外也。裳内缝者。反其制也。哀藏于内也。上衣为阳。下裳为阴。阴主敛蓄而阳主发露也。
在室女。谓许嫁而已笄者未及行也。
女出嫁而不易父祖。男之出后则父祖易矣。恐不可相方。
记曰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缌。后儒因此而别生意见。以为有甥之依乎外家者。见其从母之夫舅之妻亦同居而有死者。疑其服而论之也。是以或者曰同爨则可服缌云尔。然从母之夫。初非妇人。而今谓二夫人。岂成说乎。鄙意则以为此是三种人也。非止二人也。盖甥之于从母之夫及舅之妻。本皆无服。而今或同爨则可以缌也。二夫人。如赵衰之叔隈赵姬。晋时之有左右夫人也。王毖吴纲皆有两妻。此固不常有者。而亦或有时而遭此。则二夫人地均位敌。不可以相妾。而亦不可以制为相服之节。然其或同爨则可以缌也。凡此三种人。异居则皆无服。同居则不得不为之缌也。记之意本自如此。而却被注家错乱了。寻常可讶。
古礼朝夕奠。只有哭踊而无拜。馈食则并无哭拜之节。家礼朝夕奠。始有再拜之文。上食曰如朝奠仪。其并有拜可知。然终不若古礼之有精义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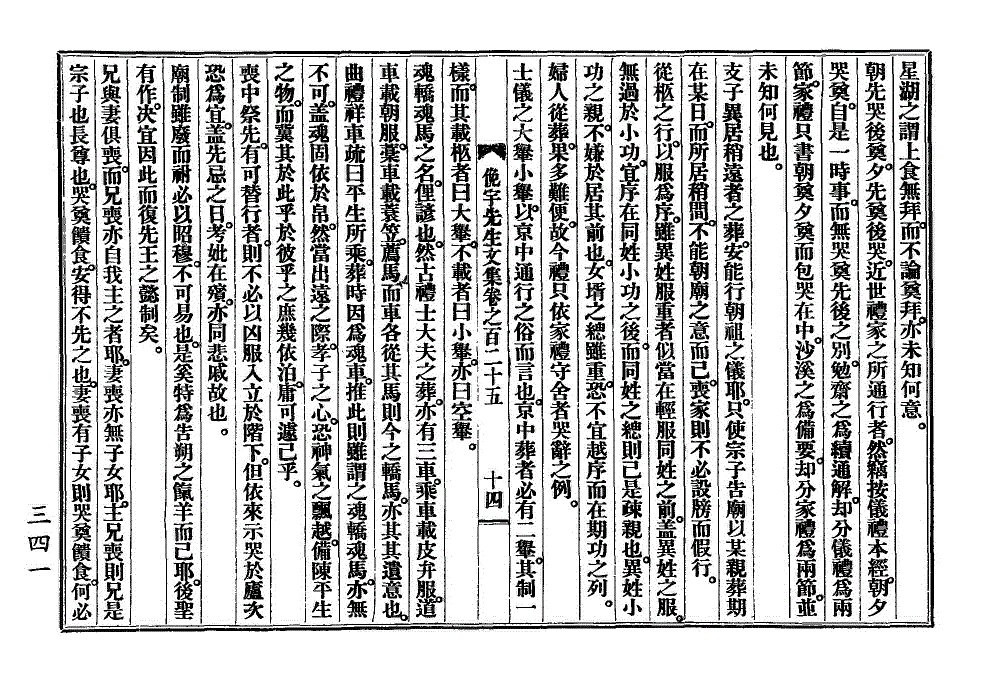 星湖之谓上食无拜。而不论奠拜。亦未知何意。
星湖之谓上食无拜。而不论奠拜。亦未知何意。朝先哭后奠。夕先奠后哭。近世礼家之所通行者。然窃按仪礼本经。朝夕哭奠。自是一时事。而无哭奠先后之别。勉斋之为续通解。却分仪礼为两节。家礼只书朝奠夕奠而包哭在中。沙溪之为备要。却分家礼为两节。并未知何见也。
支子异居稍远者之葬。安能行朝祖之仪耶。只使宗子告庙以某亲葬期在某日。而所居稍间。不能朝庙之意而已。丧家则不必设榜而假行。
从柩之行。以服为序。虽异姓服重者似当在轻服同姓之前。盖异姓之服。无过于小功。宜序在同姓小功之后。而同姓之缌则已是疏亲也。异姓小功之亲。不嫌于居其前也。女婿之缌虽重。恐不宜越序而在期功之列。
妇人从葬。果多难便。故今礼只依家礼守舍者哭辞之例。
士仪之大舆小舆。以京中通行之俗而言也。京中葬者必有二舆。其制一样。而其载柩者曰大舆。不载者曰小舆。亦曰空舆。
魂轿魂马之名。俚谚也。然古礼士大夫之葬。亦有三车。乘车载皮弁服。道车载朝服。藁车载蓑笠。荐马而车各从其马则今之轿马。亦其其遗意也。曲礼祥车疏曰平生所乘。葬时因为魂车。推此则虽谓之魂轿魂马。亦无不可。盖魂固依于帛。然当出远之际。孝子之心。恐神气之飘越。备陈平生之物。而冀其于此乎于彼乎之庶几依泊。庸可遽已乎。
丧中祭先。有可替行者。则不必以凶服入立于阶下。但依来示哭于庐次恐为宜。盖先忌之日。考妣在殡。亦同悲戚故也。
庙制虽废而祔必以昭穆。不可易也。是奚特为告朔之饩羊而已耶。后圣有作。决宜因此而复先王之懿制矣。
兄与妻俱丧。而兄丧亦自我主之者耶。妻丧亦无子女耶。主兄丧则兄是宗子也长尊也。哭奠馈食。安得不先之也。妻丧有子女则哭奠馈食。何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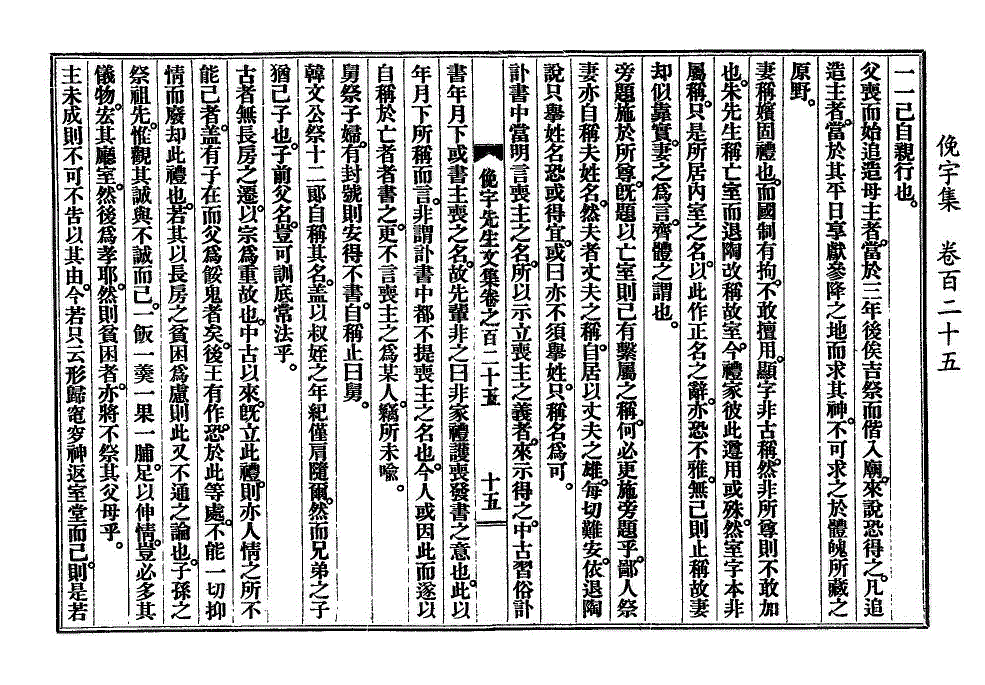 一一己自亲行也。
一一己自亲行也。父丧而始追造母主者。当于三年后俟吉祭而偕入庙。来说恐得之。凡追造主者。当于其平日享献参降之地而求其神。不可求之于体魄所藏之原野。
妻称嫔固礼也。而国制有拘。不敢擅用。显字非古称。然非所尊则不敢加也。朱先生称亡室而退陶改称故室。今礼家彼此遵用或殊。然室字本非属称。只是所居内室之名。以此作正名之辞。亦恐不雅。无已则止称故妻却似靠实。妻之为言。齐体之谓也。
旁题施于所尊。既题以亡室则已有系属之称。何必更施旁题乎。鄙人祭妻亦自称夫姓名。然夫者丈夫之称。自居以丈夫之雄。每切难安。依退陶说只举姓名恐或得宜。或曰亦不须举姓。只称名为可。
讣书中当明言丧主之名。所以示立丧主之义者。来示得之。中古习俗讣书年月下或书主丧之名。故先辈非之曰非家礼护丧发书之意也。此以年月下所称而言。非谓讣书中都不提丧主之名也。今人或因此而遂以自称于亡者者书之。更不言丧主之为某人。窃所未喻。
舅祭子妇。有封号则安得不书。自称止曰舅。
韩文公祭十二郎自称其名。盖以叔侄之年纪仅肩随尔。然而兄弟之子犹己子也。子前父名。岂可训底常法乎。
古者无长房之迁。以宗为重故也。中古以来。既立此礼。则亦人情之所不能已者。盖有子在而父为馁鬼者矣。后王有作。恐于此等处。不能一切抑情而废却此礼也。若其以长房之贫困为虑则此又不通之论也。子孙之祭祖先。惟观其诚与不诚而已。一饭一羹一果一脯。足以伸情。岂必多其仪物。宏其厅室。然后为孝耶。然则贫困者。亦将不祭其父母乎。
主未成则不可不告以其由。今若只云形归窀穸神返室堂而已。则是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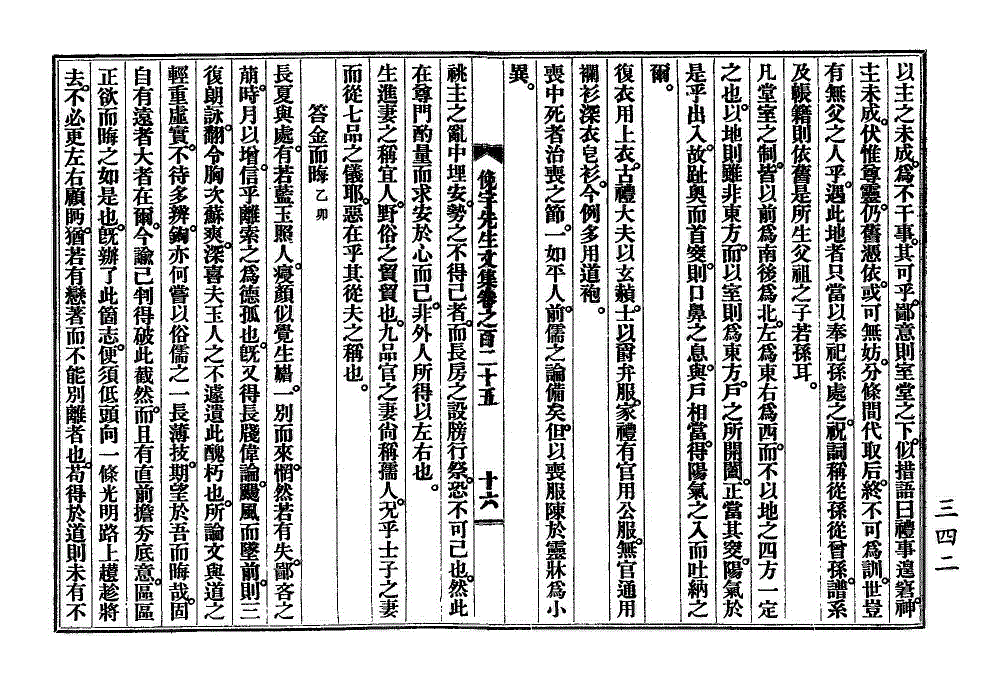 以主之未成。为不干事。其可乎。鄙意则室堂之下。似措语曰礼事遑窘。神主未成。伏惟尊灵。仍旧凭依。或可无妨。分条间代取后。终不可为训。世岂有无父之人乎。遇此地者只当以奉祀孙处之。祝词称从孙从曾孙。谱系及帐籍则依旧是所生父祖之子若孙耳。
以主之未成。为不干事。其可乎。鄙意则室堂之下。似措语曰礼事遑窘。神主未成。伏惟尊灵。仍旧凭依。或可无妨。分条间代取后。终不可为训。世岂有无父之人乎。遇此地者只当以奉祀孙处之。祝词称从孙从曾孙。谱系及帐籍则依旧是所生父祖之子若孙耳。凡堂室之制。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而不以地之四方一定之也。以地则虽非东方。而以室则为东方。户之所开阖。正当其窔。阳气于是乎出入。故趾奥而首窔。则口鼻之息。与户相当。得阳气之入而吐纳之尔。
复衣用上衣。古礼大夫以玄赪。士以爵弁服。家礼有官用公服。无官通用襕衫深衣皂衫。今例多用道袍。
丧中死者治丧之节。一如平人。前儒之论备矣。但以丧服陈于灵床为小异。
祧主之乱中埋安。势之不得已者。而长房之设榜行祭。恐不可已也。然此在尊门酌量而求安于心而已。非外人所得以左右也。
生进妻之称宜人。野俗之贸贸也。九品官之妻尚称孺人。况乎士子之妻而从七品之仪耶。恶在乎其从夫之称也。
答金而晦(乙卯)
长夏与处。有若蓝玉照人。㾛颜似觉生媚。一别而来。惘然若有失。鄙吝之萌。时月以增。信乎离索之为德孤也。既又得长笺伟论。飏风而坠前。则三复朗咏。翻令胸次苏爽。深喜夫玉人之不遽遗此丑朽也。所论文与道之轻重虚实。不待多辨。鋾亦何尝以俗儒之一长薄技。期望于吾而晦哉。固自有远者大者在尔。今谕已判得破此截然。而且有直前担夯底意。区区正欲而晦之如是也。既办了此个志。便须低头向一条光明路上趱趁将去。不必更左右顾眄。犹若有恋著而不能别离者也。苟得于道则未有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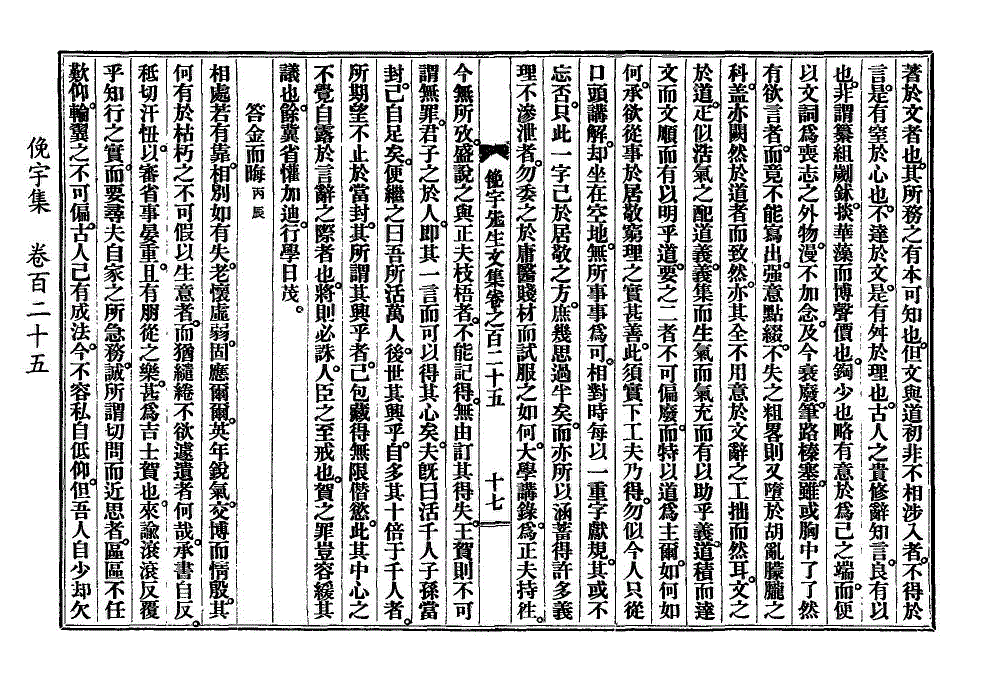 著于文者也。其所务之有本可知也。但文与道初非不相涉入者。不得于言。是有窒于心也。不达于文。是有舛于理也。古人之贵修辞知言。良有以也。非谓纂组刿鉥。掞华藻而博声价也。鋾少也略有意于为己之端。而便以文词为丧志之外物。漫不加念。及今衰废。笔路榛塞。虽或胸中了了然有欲言者。而竟不能写出。强意点缀。不失之粗略则又堕于胡乱朦胧之科。盖亦阙然于道者而致然。亦其全不用意于文辞之工拙而然耳。文之于道。疋似浩气之配道义。义集而生气而气充而有以助乎义。道积而达文而文顺而有以明乎道。要之二者不可偏废。而特以道为主尔。如何如何。承欲从事于居敬穷理之实甚善。此须实下工夫乃得。勿似今人只从口头讲解。却坐在空地。无所事事为可。相对时每以一重字献规。其或不忘否。只此一字已于居敬之方。庶几思过半矣。而亦所以涵蓄得许多义理不渗泄者。勿委之于庸医贱材而试服之如何。大学讲录。为正夫持往。今无所考。盛说之与正夫枝梧者。不能记得。无由订其得失。王贺则不可谓无罪。君子之于人。即其一言而可以得其心矣。夫既曰活千人子孙当封。已自足矣。便继之曰吾所活万人。后世其兴乎。自多其十倍于千人者。所期望不止于当封。其所谓其兴乎者。已包藏得无限僭欲。此其中心之不觉自露于言辞之际者也。将则必诛。人臣之至戒也。贺之罪岂容缓其议也。馀冀省欢加迪。行学日茂。
著于文者也。其所务之有本可知也。但文与道初非不相涉入者。不得于言。是有窒于心也。不达于文。是有舛于理也。古人之贵修辞知言。良有以也。非谓纂组刿鉥。掞华藻而博声价也。鋾少也略有意于为己之端。而便以文词为丧志之外物。漫不加念。及今衰废。笔路榛塞。虽或胸中了了然有欲言者。而竟不能写出。强意点缀。不失之粗略则又堕于胡乱朦胧之科。盖亦阙然于道者而致然。亦其全不用意于文辞之工拙而然耳。文之于道。疋似浩气之配道义。义集而生气而气充而有以助乎义。道积而达文而文顺而有以明乎道。要之二者不可偏废。而特以道为主尔。如何如何。承欲从事于居敬穷理之实甚善。此须实下工夫乃得。勿似今人只从口头讲解。却坐在空地。无所事事为可。相对时每以一重字献规。其或不忘否。只此一字已于居敬之方。庶几思过半矣。而亦所以涵蓄得许多义理不渗泄者。勿委之于庸医贱材而试服之如何。大学讲录。为正夫持往。今无所考。盛说之与正夫枝梧者。不能记得。无由订其得失。王贺则不可谓无罪。君子之于人。即其一言而可以得其心矣。夫既曰活千人子孙当封。已自足矣。便继之曰吾所活万人。后世其兴乎。自多其十倍于千人者。所期望不止于当封。其所谓其兴乎者。已包藏得无限僭欲。此其中心之不觉自露于言辞之际者也。将则必诛。人臣之至戒也。贺之罪岂容缓其议也。馀冀省欢加迪。行学日茂。答金而晦(丙辰)
相处若有靠。相别如有失。老怀虚弱。固应尔尔。英年锐气。交博而情殷。其何有于枯朽之不可假以生意者。而犹缱绻不欲遽遗者何哉。承书自反。秪切汗忸。以审省事晏重。且有朋从之乐。甚为吉士贺也。来谕滚滚反覆乎知行之实。而要寻夫自家之所急务。诚所谓切问而近思者。区区不任叹仰。轮翼之不可偏。古人已有成法。今不容私自低仰。但吾人自少却欠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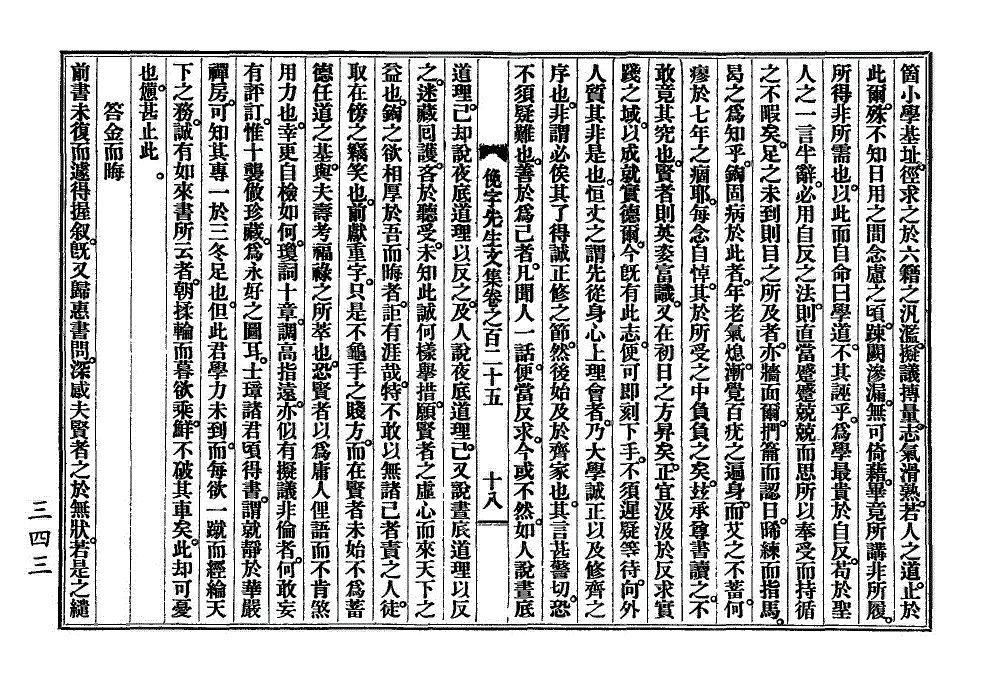 个小学基址。径求之于六籍之汎滥。拟议抟量。志气滑熟。若人之道。止于此尔。殊不知日用之间念虑之顷。疏阙渗漏。无可倚藉。毕竟所讲非所履。所得非所需也。以此而自命曰学道。不其诬乎。为学最贵于自反。苟于圣人之一言半辞。必用自反之法。则直当蹙蹙兢兢而思所以奉受而持循之不暇矣。足之未到则目之所及者。亦墙面尔。扪籥而认日。晞练而指马。曷之为知乎。鋾固病于此者。年老气熄。渐觉百疣之遍身。而艾之不蓄。何瘳于七年之痼耶。每念自悼。其于所受之中负负之矣。玆承尊书读之。不敢竟其究也。贤者则英姿富识。又在初日之方升矣。正宜汲汲于反求实践之域。以成就实德尔。今既有此志。便可即刻下手。不须迟疑等待。向外人质其非是也。恒丈之谓先从身心上理会者。乃大学诚正以及修齐之序也。非谓必俟其了得诚正修之节。然后始及于齐家也。其言甚警切。恐不须疑难也。善于为己者。凡闻人一话。便当反求。今或不然。如人说昼底道理。己却说夜底道理以反之。及人说夜底道理。己又说昼底道理以反之。迷藏回护。吝于听受。未知此诚何样举措。愿贤者之虚心而来天下之益也。鋾之欲相厚于吾而晦者。讵有涯哉。特不敢以无诸己者责之人。徒取在傍之窃笑也。前献重字。只是不龟手之贱方。而在贤者未始不为蓄德任道之基。与夫寿考福禄之所萃也。恐贤者以为庸人俚语而不肯煞用力也。幸更自检如何。琼词十章。调高指远。亦似有拟议非伦者。何敢妄有评订。惟十袭做珍藏。为永好之图耳。士璋诸君顷得书。谓就静于华严禅房。可知其专一于三冬足也。但此君学力未到。而每欲一蹴而经纶天下之务。诚有如来书所云者。朝揉轮而暮欲乘。鲜不破其车矣。此却可忧也。惫甚止此。
个小学基址。径求之于六籍之汎滥。拟议抟量。志气滑熟。若人之道。止于此尔。殊不知日用之间念虑之顷。疏阙渗漏。无可倚藉。毕竟所讲非所履。所得非所需也。以此而自命曰学道。不其诬乎。为学最贵于自反。苟于圣人之一言半辞。必用自反之法。则直当蹙蹙兢兢而思所以奉受而持循之不暇矣。足之未到则目之所及者。亦墙面尔。扪籥而认日。晞练而指马。曷之为知乎。鋾固病于此者。年老气熄。渐觉百疣之遍身。而艾之不蓄。何瘳于七年之痼耶。每念自悼。其于所受之中负负之矣。玆承尊书读之。不敢竟其究也。贤者则英姿富识。又在初日之方升矣。正宜汲汲于反求实践之域。以成就实德尔。今既有此志。便可即刻下手。不须迟疑等待。向外人质其非是也。恒丈之谓先从身心上理会者。乃大学诚正以及修齐之序也。非谓必俟其了得诚正修之节。然后始及于齐家也。其言甚警切。恐不须疑难也。善于为己者。凡闻人一话。便当反求。今或不然。如人说昼底道理。己却说夜底道理以反之。及人说夜底道理。己又说昼底道理以反之。迷藏回护。吝于听受。未知此诚何样举措。愿贤者之虚心而来天下之益也。鋾之欲相厚于吾而晦者。讵有涯哉。特不敢以无诸己者责之人。徒取在傍之窃笑也。前献重字。只是不龟手之贱方。而在贤者未始不为蓄德任道之基。与夫寿考福禄之所萃也。恐贤者以为庸人俚语而不肯煞用力也。幸更自检如何。琼词十章。调高指远。亦似有拟议非伦者。何敢妄有评订。惟十袭做珍藏。为永好之图耳。士璋诸君顷得书。谓就静于华严禅房。可知其专一于三冬足也。但此君学力未到。而每欲一蹴而经纶天下之务。诚有如来书所云者。朝揉轮而暮欲乘。鲜不破其车矣。此却可忧也。惫甚止此。答金而晦
前书未复而遽得握叙。既又归惠书问。深感夫贤者之于无状。若是之缱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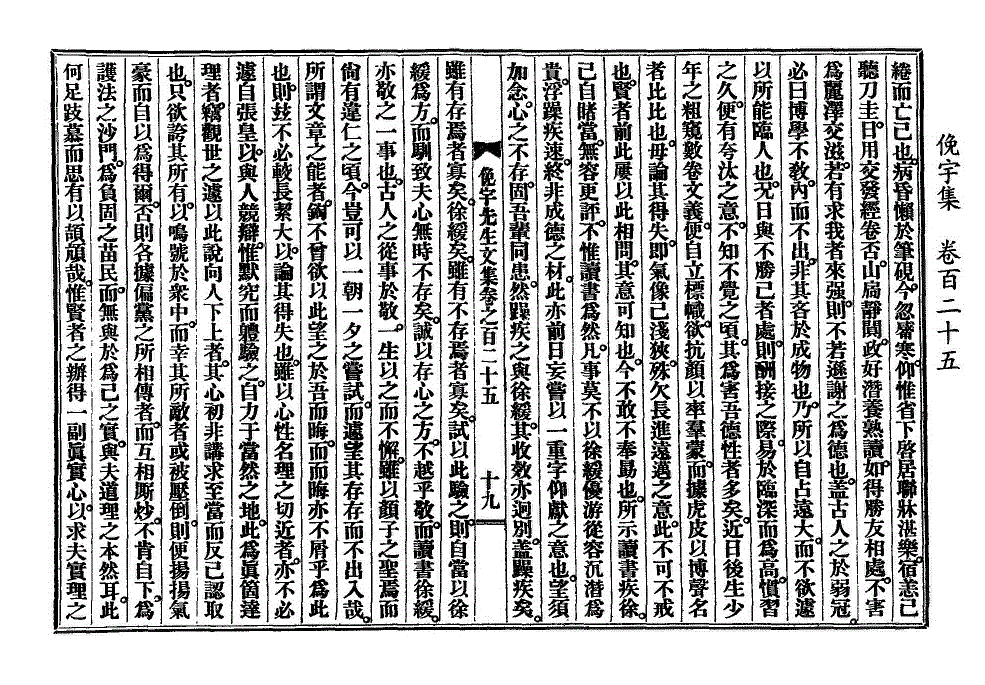 绻而亡已也。病昏懒于笔砚。今忽觱寒。仰惟省下启居联床湛乐。宿恙已听刀圭。日用交发经卷否。山扃静阒。政好潜养熟读。如得胜友相处。不害为丽泽交滋。若有求我者来强。则不若逊谢之为德也。盖古人之于弱冠。必曰博学不教。内而不出。非其吝于成物也。乃所以自占远大。而不欲遽以所能临人也。况日与不胜己者处。则酬接之际。易于临深而为高。惯习之久。便有夸汰之意。不知不觉之顷。其为害吾德性者多矣。近日后生少年之粗窥数卷文义。便自立标帜。欲抗颜以率群蒙。而据虎皮以博声名者比比也。毋论其得失。即气像已浅狭。殊欠长进远迈之意。此不可不戒也。贤者前此屡以此相问。其意可知也。今不敢不奉勖也。所示读书疾徐。已自睹当。无容更评。不惟读书为然。凡事莫不以徐缓优游从容沉潜为贵。浮躁疾速。终非成德之材。此亦前日妄尝以一重字仰献之意也。望须加念。心之不存。固吾辈同患。然躁疾之与徐缓。其收效亦迥别。盖躁疾矣。虽有存焉者寡矣。徐缓矣。虽有不存焉者寡矣。试以此验之。则自当以徐缓为方。而驯致夫心无时不存矣。诚以存心之方。不越乎敬。而读书徐缓。亦敬之一事也。古人之从事于敬。一生以之而不懈。虽以颜子之圣焉而尚有违仁之顷。今岂可以一朝一夕之尝试。而遽望其存存而不出入哉。所谓文章之能者。鋾不曾欲以此望之于吾而晦。而而晦亦不屑乎为此也。则玆不必较长絜大。以论其得失也。虽以心性名理之切近者。亦不必遽自张皇。以与人竞辩。惟默究而体验之。自力于当然之地。此为真个达理者。窃观世之遽以此说向人下上者。其心初非讲求至当而反己认取也。只欲誇其所有。以鸣号于众中。而幸其所敌者或被压倒。则便扬扬气豪而自以为得尔。否则各据偏党之所相传者。而互相厮炒。不肯自下。为护法之沙门。为负固之苗民。而无与于为己之实。与夫道理之本然耳。此何足跂慕而思有以颉颃哉。惟贤者之办得一副真实心。以求夫实理之
绻而亡已也。病昏懒于笔砚。今忽觱寒。仰惟省下启居联床湛乐。宿恙已听刀圭。日用交发经卷否。山扃静阒。政好潜养熟读。如得胜友相处。不害为丽泽交滋。若有求我者来强。则不若逊谢之为德也。盖古人之于弱冠。必曰博学不教。内而不出。非其吝于成物也。乃所以自占远大。而不欲遽以所能临人也。况日与不胜己者处。则酬接之际。易于临深而为高。惯习之久。便有夸汰之意。不知不觉之顷。其为害吾德性者多矣。近日后生少年之粗窥数卷文义。便自立标帜。欲抗颜以率群蒙。而据虎皮以博声名者比比也。毋论其得失。即气像已浅狭。殊欠长进远迈之意。此不可不戒也。贤者前此屡以此相问。其意可知也。今不敢不奉勖也。所示读书疾徐。已自睹当。无容更评。不惟读书为然。凡事莫不以徐缓优游从容沉潜为贵。浮躁疾速。终非成德之材。此亦前日妄尝以一重字仰献之意也。望须加念。心之不存。固吾辈同患。然躁疾之与徐缓。其收效亦迥别。盖躁疾矣。虽有存焉者寡矣。徐缓矣。虽有不存焉者寡矣。试以此验之。则自当以徐缓为方。而驯致夫心无时不存矣。诚以存心之方。不越乎敬。而读书徐缓。亦敬之一事也。古人之从事于敬。一生以之而不懈。虽以颜子之圣焉而尚有违仁之顷。今岂可以一朝一夕之尝试。而遽望其存存而不出入哉。所谓文章之能者。鋾不曾欲以此望之于吾而晦。而而晦亦不屑乎为此也。则玆不必较长絜大。以论其得失也。虽以心性名理之切近者。亦不必遽自张皇。以与人竞辩。惟默究而体验之。自力于当然之地。此为真个达理者。窃观世之遽以此说向人下上者。其心初非讲求至当而反己认取也。只欲誇其所有。以鸣号于众中。而幸其所敌者或被压倒。则便扬扬气豪而自以为得尔。否则各据偏党之所相传者。而互相厮炒。不肯自下。为护法之沙门。为负固之苗民。而无与于为己之实。与夫道理之本然耳。此何足跂慕而思有以颉颃哉。惟贤者之办得一副真实心。以求夫实理之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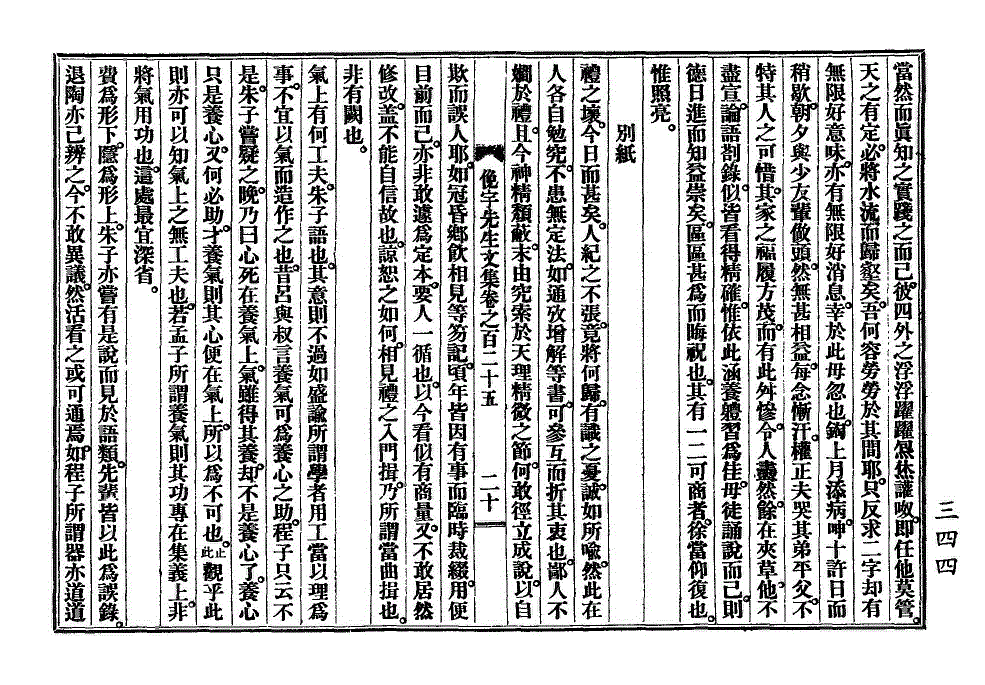 当然而真知之实践之而已。彼四外之浮浮跃跃炰炰欢呶。即任他莫管。天之有定。必将水流而归壑矣。吾何容劳劳于其间耶。只反求二字却有无限好意味。亦有无限好消息。幸于此毋忽也。鋾上月添病。呻十许日而稍歇。朝夕与少友辈做头。然无甚相益。每念惭汗。权正夫哭其弟平父。不特其人之可惜。其家之福履方茂。而有此舛惨。令人䀌然。馀在夹草。他不尽宣。论语劄录。似皆看得精确。惟依此涵养体习为佳。毋徒诵说而已。则德日进而知益崇矣。区区甚为而晦祝也。其有一二可商者。徐当仰复也。惟照亮。
当然而真知之实践之而已。彼四外之浮浮跃跃炰炰欢呶。即任他莫管。天之有定。必将水流而归壑矣。吾何容劳劳于其间耶。只反求二字却有无限好意味。亦有无限好消息。幸于此毋忽也。鋾上月添病。呻十许日而稍歇。朝夕与少友辈做头。然无甚相益。每念惭汗。权正夫哭其弟平父。不特其人之可惜。其家之福履方茂。而有此舛惨。令人䀌然。馀在夹草。他不尽宣。论语劄录。似皆看得精确。惟依此涵养体习为佳。毋徒诵说而已。则德日进而知益崇矣。区区甚为而晦祝也。其有一二可商者。徐当仰复也。惟照亮。别纸
礼之壤。今日而甚矣。人纪之不张。竟将何归。有识之忧。诚如所喻。然此在人各自勉究。不患无定法。如通考增解等书。可参互而折其衷也。鄙人不娴于礼。且今神精颓蔽。末由究索于天理精微之节。何敢径立成说。以自欺而误人耶。如冠昏乡饮相见等笏记。顷年皆因有事而临时裁缀。用便目前而已。亦非敢遽为定本。要人一循也。以今看似有商量。又不敢居然修改。盖不能自信故也。谅恕之如何。相见礼之入门揖。乃所谓当曲揖也。非有阙也。
气上有何工夫。朱子语也。其意则不过如盛谕所谓学者用工当以理为事。不宜以气而造作之也。昔吕与叔言养气可为养心之助。程子只云不是。朱子尝疑之。晚乃曰心死在养气上。气虽得其养。却不是养心了。养心只是养心。又何必助。才养气则其心便在气上。所以为不可也。(止此)观乎此则亦可以知气上之无工夫也。若孟子所谓养气则其功专在集义上。非将气用功也。这处最宜深省。
费为形下。隐为形上。朱子亦尝有是说而见于语类。先辈皆以此为误录。退陶亦已辨之。今不敢异议。然活看之或可通焉。如程子所谓器亦道道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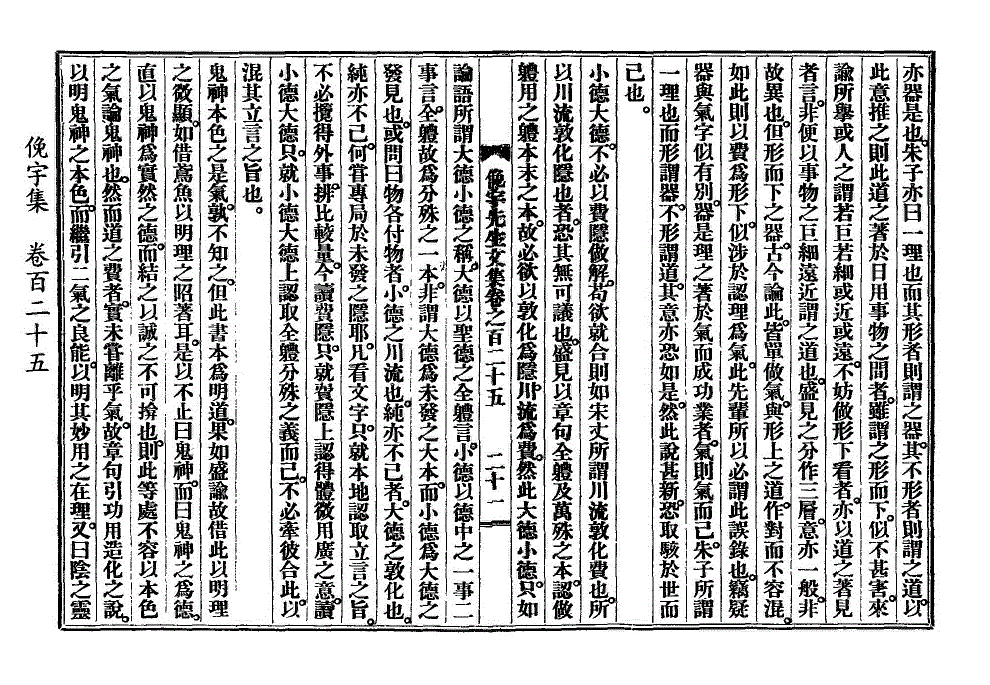 亦器是也。朱子亦曰一理也而其形者则谓之器。其不形者则谓之道。以此意推之则此道之著于日用事物之间者。虽谓之形而下。似不甚害。来谕所举或人之谓若巨若细或近或远。不妨做形下看者。亦以道之著见者言。非便以事物之巨细远近谓之道也。盛见之分作三层。意亦一般。非故异也。但形而下之器。古今论此。皆单做气。与形上之道。作对而不容混。如此则以费为形下。似涉于认理为气。此先辈所以必谓此误录也。窃疑器与气字似有别。器是理之著于气而成功业者。气则气而已。朱子所谓一理也而形谓器。不形谓道。其意亦恐如是。然此说甚新。恐取骇于世而已也。
亦器是也。朱子亦曰一理也而其形者则谓之器。其不形者则谓之道。以此意推之则此道之著于日用事物之间者。虽谓之形而下。似不甚害。来谕所举或人之谓若巨若细或近或远。不妨做形下看者。亦以道之著见者言。非便以事物之巨细远近谓之道也。盛见之分作三层。意亦一般。非故异也。但形而下之器。古今论此。皆单做气。与形上之道。作对而不容混。如此则以费为形下。似涉于认理为气。此先辈所以必谓此误录也。窃疑器与气字似有别。器是理之著于气而成功业者。气则气而已。朱子所谓一理也而形谓器。不形谓道。其意亦恐如是。然此说甚新。恐取骇于世而已也。小德大德。不必以费隐做解。苟欲就合则如宋丈所谓川流敦化费也。所以川流敦化隐也者。恐其无可议也。盛见以章句全体及万殊之本。认做体用之体本末之本。故必欲以敦化为隐。川流为费。然此大德小德。只如论语所谓大德小德之称。大德以圣德之全体言。小德以德中之一事二事言。全体故为分殊之一本。非谓大德为未发之大本。而小德为大德之发见也。或问曰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也。纯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纯亦不已。何尝专局于未发之隐耶。凡看文字。只就本地认取立言之旨。不必揽得外事。排比较量。今读费隐。只就费隐上认得体微用广之意。读小德大德。只就小德大德上认取全体分殊之义而已。不必牵彼合此。以混其立言之旨也。
鬼神本色之是气。孰不知之。但此书本为明道。果如盛谕故借此以明理之微显。如借鸢鱼以明理之昭著耳。是以不止曰鬼神。而曰鬼神之为德。直以鬼神为实然之德。而结之以诚之不可掩也。则此等处不容以本色之气论鬼神也。然而道之费者。实未尝离乎气。故章句引功用造化之说。以明鬼神之本色。而继引二气之良能。以明其妙用之在理。又曰阴之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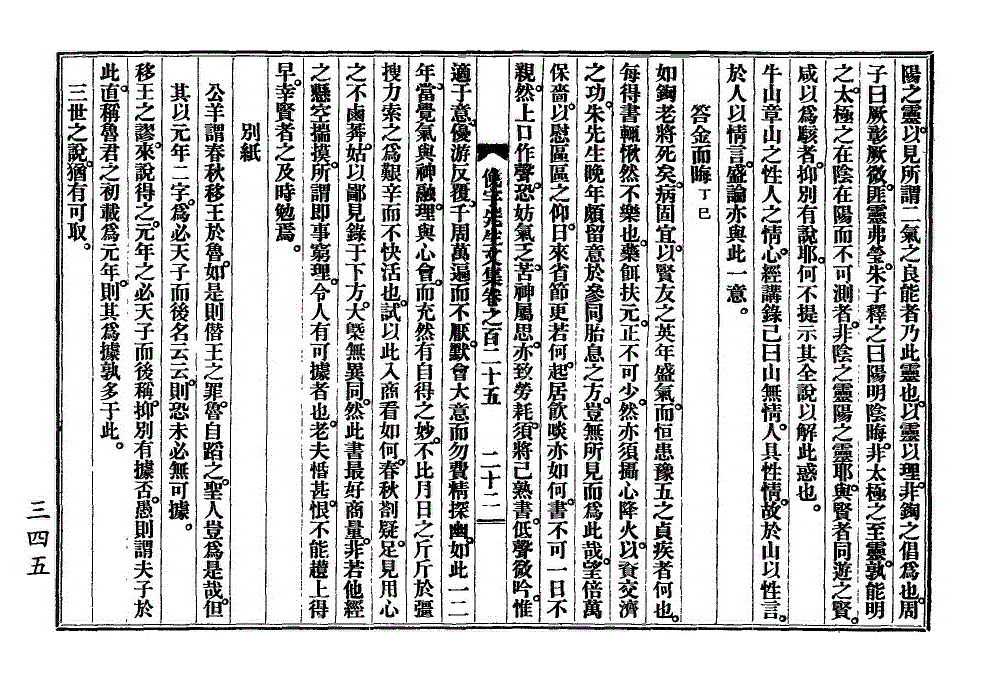 阳之灵。以见所谓二气之良能者乃此灵也。以灵以理。非鋾之倡为也。周子曰厥彰厥微。匪灵弗莹。朱子释之曰阳明阴晦。非太极之至灵。孰能明之。太极之在阴在阳而不可测者。非阴之灵阳之灵耶。与贤者同游之贤。咸以为骇者。抑别有说耶。何不提示其全说以解此惑也。
阳之灵。以见所谓二气之良能者乃此灵也。以灵以理。非鋾之倡为也。周子曰厥彰厥微。匪灵弗莹。朱子释之曰阳明阴晦。非太极之至灵。孰能明之。太极之在阴在阳而不可测者。非阴之灵阳之灵耶。与贤者同游之贤。咸以为骇者。抑别有说耶。何不提示其全说以解此惑也。牛山章山之性人之情。心经讲录已曰山无情。人具性情。故于山以性言。于人以情言。盛论亦与此一意。
答金而晦(丁巳)
如鋾老将死矣。病固宜。以贤友之英年盛气。而恒患豫五之贞疾者何也。每得书辄愀然不乐也。药饵扶元。正不可少。然亦须摄心降火。以资交济之功。朱先生晚年颇留意于参同胎息之方。岂无所见而为此哉。望倍万保啬。以慰区区之仰。日来省节更若何。起居饮啖亦如何。书不可一日不亲。然上口作声。恐妨气乏。苦神属思。亦致劳耗。须将已熟书。低声微吟。惟适于意。优游反覆。千周万遍而不厌。默会大意而勿费精探幽。如此一二年。当觉气与神融。理与心会。而充然有自得之妙。不比月日之斤斤于彊搜力索之为艰辛而不快活也。试以此入商看如何。春秋劄疑。足见用心之不卤莽。姑以鄙见录于下方。大槩无异同。然此书最好商量。非若他经之悬空揣摸。所谓即事穷理。令人有可据者也。老夫惛甚。恨不能趱上得早。幸贤者之及时勉焉。
别纸
公羊谓春秋移王于鲁。如是则僭王之罪。鲁自蹈之。圣人岂为是哉。但其以元年二字。为必天子而后名云云。则恐未必无可据。
移王之谬。来说得之。元年之必天子而后称。抑别有据否。愚则谓夫子于此。直称鲁君之初载为元年。则其为据孰多于此。
三世之说。犹有可取。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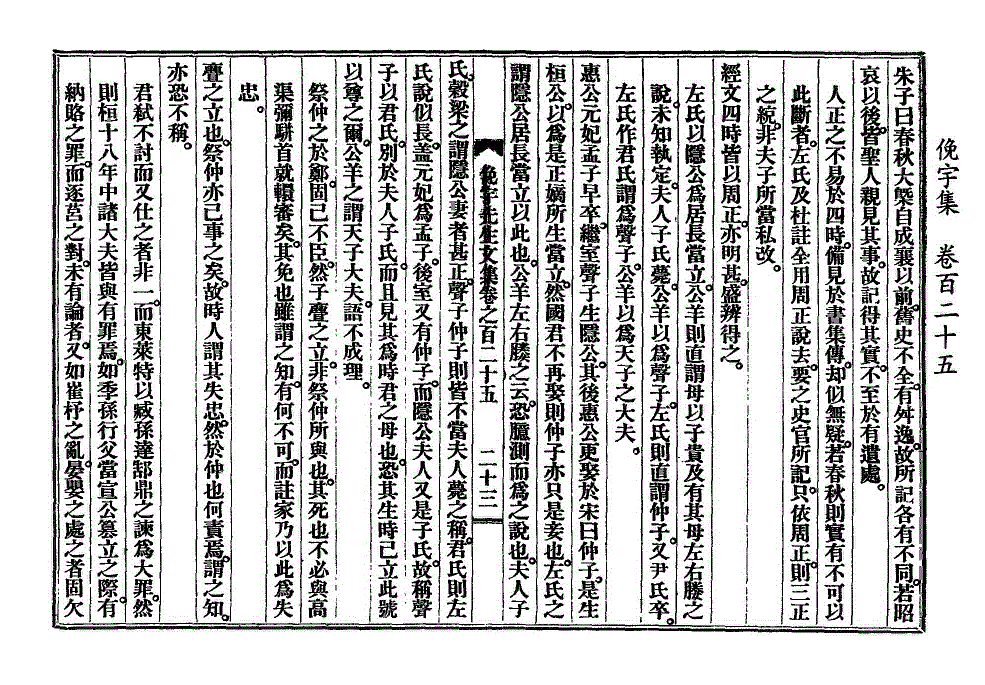 朱子曰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
朱子曰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人正之不易于四时。备见于书集传。却似无疑。若春秋则实有不可以此断者。左氏及杜注全用周正说去。要之史官所记。只依周正。则三正之统。非夫子所当私改。
经文四时皆以周正。亦明甚。盛辨得之。
左氏以隐公为居长当立。公羊则直谓母以子贵及有其母左右媵之说。未知执定。夫人子氏薨。公羊以为声子。左氏则直谓仲子。又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谓为声子。公羊以为天子之大夫。
惠公元妃孟子早卒。继室声子生隐公。其后惠公更娶于宋曰仲子。是生桓公。以为是正嫡所生当立。然国君不再娶则仲子亦只是妾也。左氏之谓隐公居长当立以此也。公羊左右媵之云。恐臆测而为之说也。夫人子氏。谷梁之谓隐公妻者甚正。声子仲子则皆不当夫人薨之称。君氏则左氏说似长。盖元妃为孟子。后室又有仲子。而隐公夫人又是子氏。故称声子以君氏。别于夫人子氏。而且见其为时君之母也。恐其生时已立此号以尊之尔。公羊之谓天子大夫。语不成理。
祭仲之于郑。固已不臣。然子亹之立。非祭仲所与也。其死也不必与高渠弥骈首就轘审矣。其免也虽谓之知。有何不可。而注家乃以此为失忠。
亹之立也。祭仲亦已事之矣。故时人谓其失忠。然于仲也何责焉。谓之知。亦恐不称。
君弑不讨而又仕之者非一。而东莱特以臧孙达郜鼎之谏为大罪。然则桓十八年中诸大夫皆与有罪焉。如季孙行父当宣公篡立之际。有纳赂之罪。而逐莒之对。未有论者。又如崔杼之乱。晏婴之处之者固欠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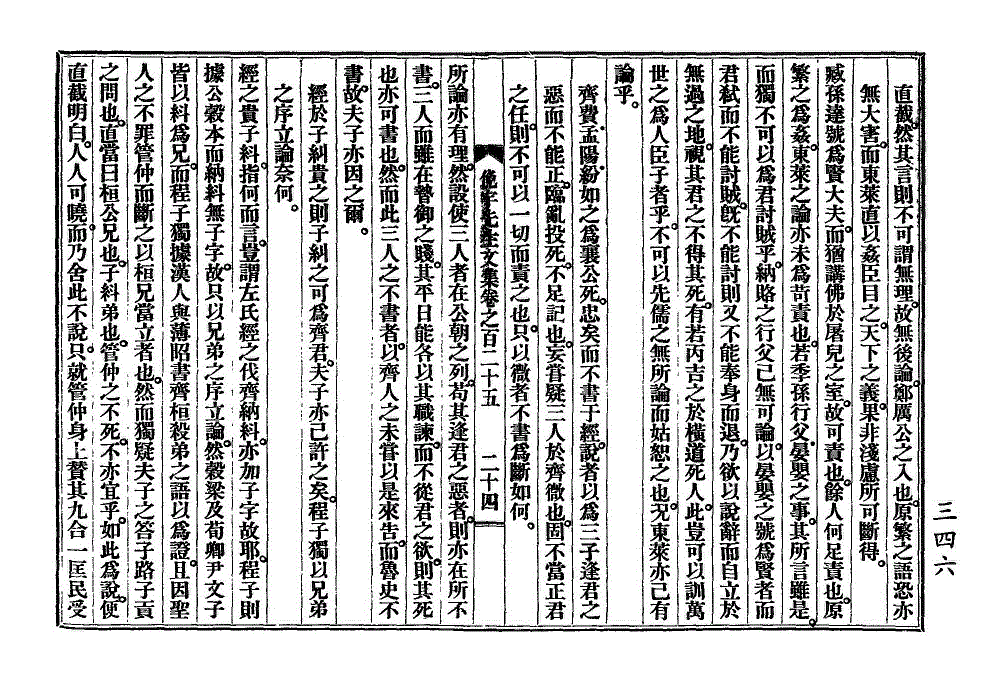 直截。然其言则不可谓无理。故无后论。郑厉公之入也。原繁之语恐亦无大害。而东莱直以奸臣目之。天下之义。果非浅虑所可断得。
直截。然其言则不可谓无理。故无后论。郑厉公之入也。原繁之语恐亦无大害。而东莱直以奸臣目之。天下之义。果非浅虑所可断得。臧孙达号为贤大夫。而犹讲佛于屠儿之室。故可责也。馀人何足责也。原繁之为奸。东莱之论亦未为苛责也。若季孙行父,晏婴之事。其所言虽是。而独不可以为君讨贼乎。纳赂之行父已无可论。以晏婴之号为贤者而君弑而不能讨贼。既不能讨则又不能奉身而退。乃欲以说辞而自立于无过之地。视其君之不得其死。有若丙吉之于横道死人。此岂可以训万世之为人臣子者乎。不可以先儒之无所论而姑恕之也。况东莱亦已有论乎。
齐费,孟阳,纷如之为襄公死。忠矣而不书于经。说者以为三子逢君之恶而不能正。临乱投死。不足记也。妄尝疑三人于齐微也。固不当正君之任。则不可以一切而责之也。只以微者不书为断如何。
所论亦有理。然设使三人者在公朝之列。苟其逢君之恶者。则亦在所不书。三人而虽在亵御之贱。其平日能各以其职谏。而不从君之欲。则其死也亦可书也。然而此三人之不书者。以齐人之未尝以是来告。而鲁史不书。故夫子亦因之尔。
经于子纠贵之则子纠之可为齐君。夫子亦已许之矣。程子独以兄弟之序立论奈何。
经之贵子纠。指何而言。岂谓左氏经之伐齐纳纠。亦加子字故耶。程子则据公谷本而纳纠无子字。故只以兄弟之序立论。然谷梁及荀卿尹文子皆以纠为兄。而程子独据汉人与薄昭书齐桓杀弟之语以为證。且因圣人之不罪管仲而断之以桓兄当立者也。然而独疑夫子之答子路子贡之问也。直当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管仲之不死。不亦宜乎。如此为说。便直截明白。人人可晓。而乃舍此不说。只就管仲身上赞其九合一匡民受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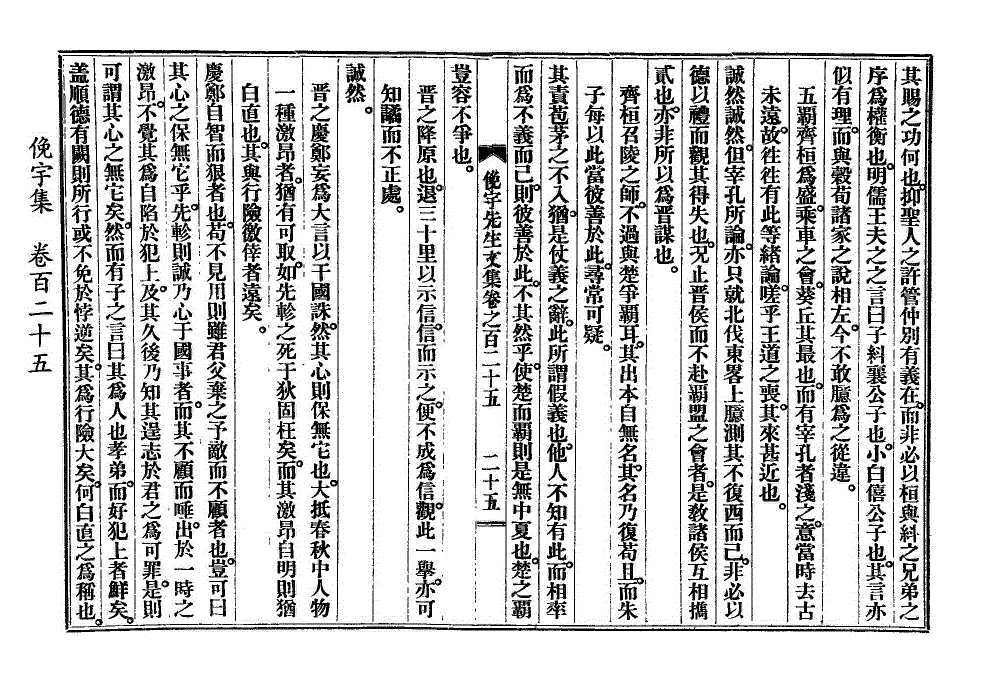 其赐之功何也。抑圣人之许管仲别有义在。而非必以桓与纠之兄弟之序为权衡也。明儒王夫之之言曰子纠襄公子也。小白僖公子也。其言亦似有理。而与谷荀诸家之说相左。今不敢臆为之从违。
其赐之功何也。抑圣人之许管仲别有义在。而非必以桓与纠之兄弟之序为权衡也。明儒王夫之之言曰子纠襄公子也。小白僖公子也。其言亦似有理。而与谷荀诸家之说相左。今不敢臆为之从违。五霸齐桓为盛。乘车之会。葵丘其最也。而有宰孔者浅之。意当时去古未远。故往往有此等绪论。嗟乎王道之丧。其来甚近也。
诚然诚然。但宰孔所论。亦只就北伐东略上臆测其不复西而已。非必以德以礼而观其得失也。况止晋侯而不赴霸盟之会者。是教诸侯互相携贰也。亦非所以为晋谋也。
齐桓召陵之师。不过与楚争霸耳。其出本自无名。其名乃复苟且。而朱子每以此当彼善于此。寻常可疑。
其责苞茅之不入。犹是仗义之辞。此所谓假义也。他人不知有此。而相率而为不义而已。则彼善于此。不其然乎。使楚而霸则是无中夏也。楚之霸岂容不争也。
晋之降原也。退三十里以示信。信而示之。便不成为信。观此一举。亦可知谲而不正处。
诚然。
晋之庆郑妄为大言以干国诛。然其心则保无它也。大抵春秋中人物一种激昂者。犹有可取。如先轸之死于狄固枉矣。而其激昂自明则犹白直也。其与行险徼倖者远矣。
庆郑自智而狠者也。苟不见用则虽君父弃之予敌而不顾者也。岂可曰其心之保无它乎。先轸则诚乃心于国事者。而其不顾而唾。出于一时之激昂。不觉其为自陷于犯上。及其久后乃知其逞志于君之为可罪。是则可谓其心之无它矣。然而有子之言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盖顺德有阙则所行或不免于悖逆矣。其为行险大矣。何白直之为称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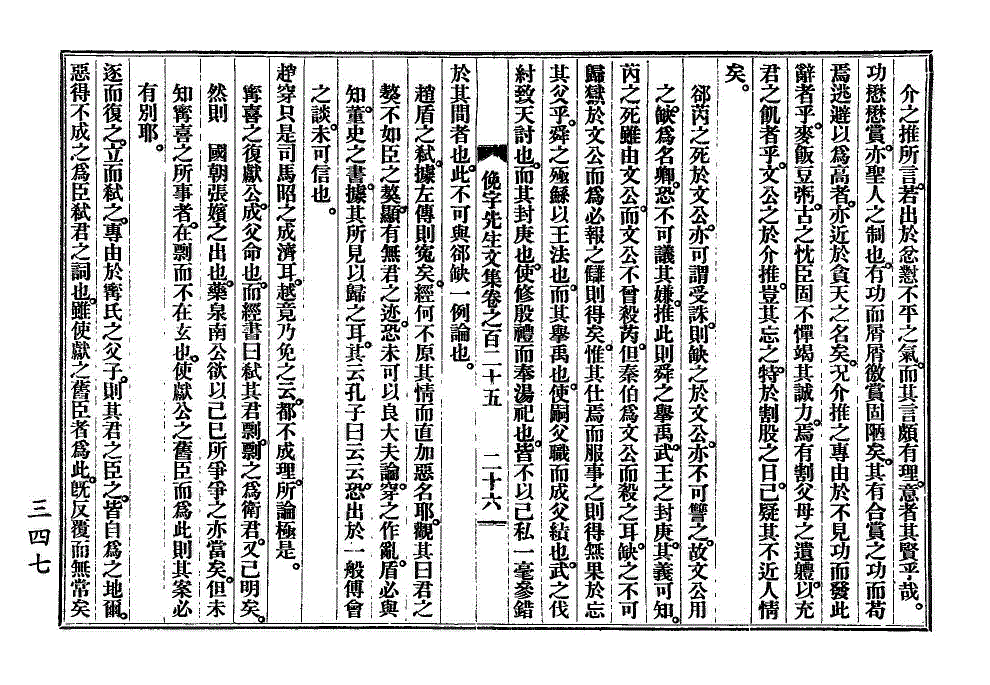 介之推所言。若出于忿怼不平之气。而其言颇有理。意者其贤乎哉。
介之推所言。若出于忿怼不平之气。而其言颇有理。意者其贤乎哉。功懋懋赏。亦圣人之制也。有功而屑屑徼赏固陋矣。其有合赏之功而苟焉逃避以为高者。亦近于贪天之名矣。况介推之专由于不见功而发此辞者乎。麦饭豆粥。古之忱臣固不惮竭其诚力。焉有割父母之遗体。以充君之饥者乎。文公之于介推。岂其忘之。特于割股之日。已疑其不近人情矣。
郤芮之死于文公。亦可谓受诛。则缺之于文公。亦不可雠之。故文公用之。缺为名卿。恐不可议其嫌。推此则舜之举禹。武王之封庚。其义可知。
芮之死虽由文公。而文公不曾杀芮。但秦伯为文公而杀之耳。缺之不可归狱于文公而为必报之雠则得矣。惟其仕焉而服事之则得无果于忘其父乎。舜之殛鲧以王法也。而其举禹也。使嗣父职而成父绩也。武之伐纣致天讨也。而其封庚也。使修殷礼而奉汤祀也。皆不以己私一毫参错于其间者也。此不可与郤缺一例论也。
赵盾之弑。据左传则冤矣。经何不原其情而直加恶名耶。观其曰君之獒不如臣之獒。显有无君之迹。恐未可以良大夫论。穿之作乱。盾必与知。董史之书。据其所见以归之耳。其云孔子曰云云。恐出于一般傅会之谈。未可信也。
赵穿只是司马昭之成济耳。越竟乃免之云。都不成理。所论极是。
宁喜之复献公。成父命也。而经书曰弑其君剽。剽之为卫君。又已明矣。然则 国朝张嫔之出也。药泉南公欲以己巳所争争之亦当矣。但未知宁喜之所事者。在剽而不在玄(一作献)也。使献公之旧臣而为此则其案必有别耶。
逐而复之。立而弑之。专由于宁氏之父子。则其君之臣之。皆自为之地尔。恶得不成之为臣弑君之词也。虽使献之旧臣者为此。既反覆而无常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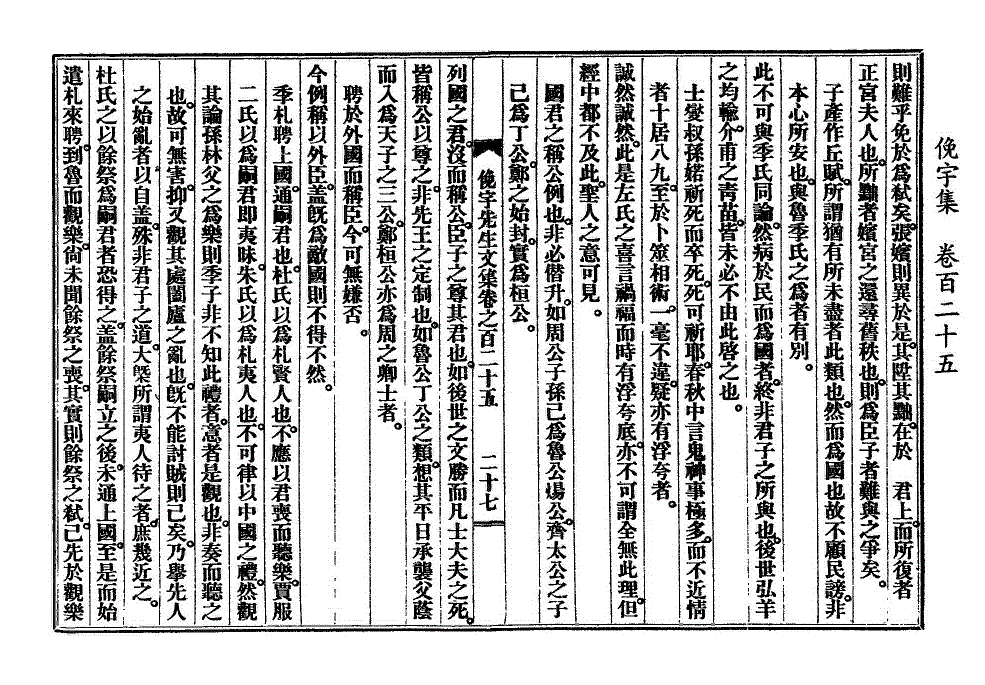 则难乎免于为弑矣。张嫔则异于是。其升其黜。在于 君上。而所复者正宫夫人也。所黜者嫔宫之还寻旧秩也。则为臣子者难与之争矣。
则难乎免于为弑矣。张嫔则异于是。其升其黜。在于 君上。而所复者正宫夫人也。所黜者嫔宫之还寻旧秩也。则为臣子者难与之争矣。子产作丘赋。所谓犹有所未尽者此类也。然而为国也故不顾民谤。非本心所安也。与鲁季氏之为者有别。
此不可与季氏同论。然病于民而为国者。终非君子之所与也。后世弘羊之均输。介甫之青苗。皆未必不由此启之也。
士燮叔孙婼祈死而卒死。死可祈耶。春秋中言鬼神事极多。而不近情者十居八九。至于卜筮相术。一毫不违。疑亦有浮夸者。
诚然诚然。此是左氏之喜言祸福而时有浮夸底。亦不可谓全无此理。但经中都不及此。圣人之意可见。
国君之称公例也。非必僭升。如周公子孙已为鲁公炀公。齐太公之子已为丁公。郑之始封。实为桓公。
列国之君。没而称公。臣子之尊其君也。如后世之文胜而凡士大夫之死。皆称公以尊之。非先王之定制也。如鲁公丁公之类。想其平日承袭父荫而入为天子之三公。郑桓公亦为周之卿士者。
聘于外国而称臣。今可无嫌否。
今例称以外臣。盖既为敌国则不得不然。
季札聘上国。通嗣君也。杜氏以为札贤人也。不应以君丧而听乐。贾服二氏以为嗣君即夷昧。朱氏以为札夷人也。不可律以中国之礼。然观其论孙林父之为乐则季子非不知此礼者。意者是观也。非奏而听之也。故可无害。抑又观其处阖庐之乱也。既不能讨贼则已矣。乃举先人之始乱者以自盖。殊非君子之道。大槩所谓夷人待之者。庶几近之。
杜氏之以馀祭为嗣君者恐得之。盖馀祭嗣立之后。未通上国。至是而始遣札来聘。到鲁而观乐。尚未闻馀祭之丧。其实则馀祭之弑。已先于观乐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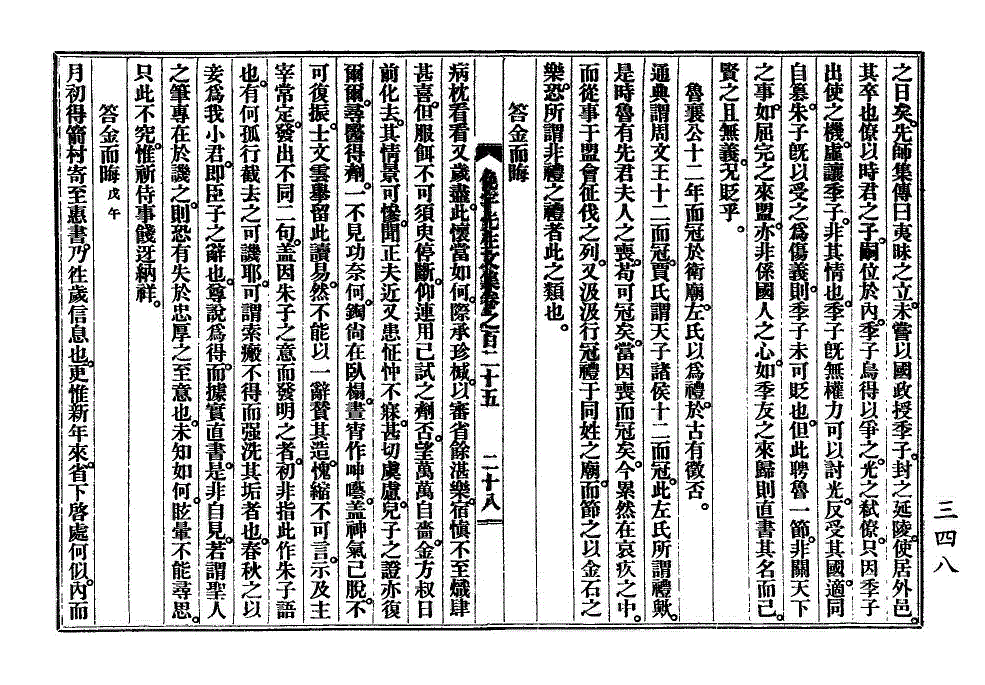 之日矣。先师集传曰夷昧之立。未尝以国政授季子。封之延陵。使居外邑。其卒也僚以时君之子。嗣位于内。季子乌得以争之。光之弑僚。只因季子出使之机。虚让季子。非其情也。季子既无权力可以讨光。反受其国。适同自篡。朱子既以受之为伤义。则季子未可贬也。但此聘鲁一节。非关天下之事。如屈完之来盟。亦非系国人之心。如季友之来归则直书其名而已。贤之且无义。况贬乎。
之日矣。先师集传曰夷昧之立。未尝以国政授季子。封之延陵。使居外邑。其卒也僚以时君之子。嗣位于内。季子乌得以争之。光之弑僚。只因季子出使之机。虚让季子。非其情也。季子既无权力可以讨光。反受其国。适同自篡。朱子既以受之为伤义。则季子未可贬也。但此聘鲁一节。非关天下之事。如屈完之来盟。亦非系国人之心。如季友之来归则直书其名而已。贤之且无义。况贬乎。鲁襄公十二年而冠于卫庙。左氏以为礼。于古有徵否。
通典谓周文王十二而冠。贾氏谓天子诸侯十二而冠。此左氏所谓礼欤。是时鲁有先君夫人之丧。苟可冠矣。当因丧而冠矣。今累然在哀疚之中。而从事于盟会征伐之列。又汲汲行冠礼于同姓之庙。而节之以金石之乐。恐所谓非礼之礼者此之类也。
答金而晦
病枕看看又岁尽。此怀当如何。际承珍椷。以审省馀湛乐。宿慎不至炽肆甚喜。但服饵不可须臾停断。仰(一作抑)连用已试之剂否。望万万自啬。金方叔日前化去。其情景可惨。闻正夫近又患怔忡不寐。甚切虞虑。儿子之證亦复尔尔。寻医得剂。一不见功奈何。鋾尚在卧榻。昼宵作呻呓。盖神气已脱。不可复振。士文云举留此读易。然不能以一辞赞其造。愧缩不可言。示及主宰常定。发出不同二句。盖因朱子之意而发明之者。初非指此作朱子语也。有何孤行截去之可讥耶。可谓索瘢不得而强洗其垢者也。春秋之以妾为我小君。即臣子之辞也。尊说为得。而据实直书。是非自见。若谓圣人之笔专在于讥之。则恐有失于忠厚之至意也。未知如何。眩晕不能寻思。只此不究。惟祈侍事饯迓纳祥。
答金而晦(戊午)
月初得箭村寄至惠书。乃往岁信息也。更惟新年来。省下启处何似。内而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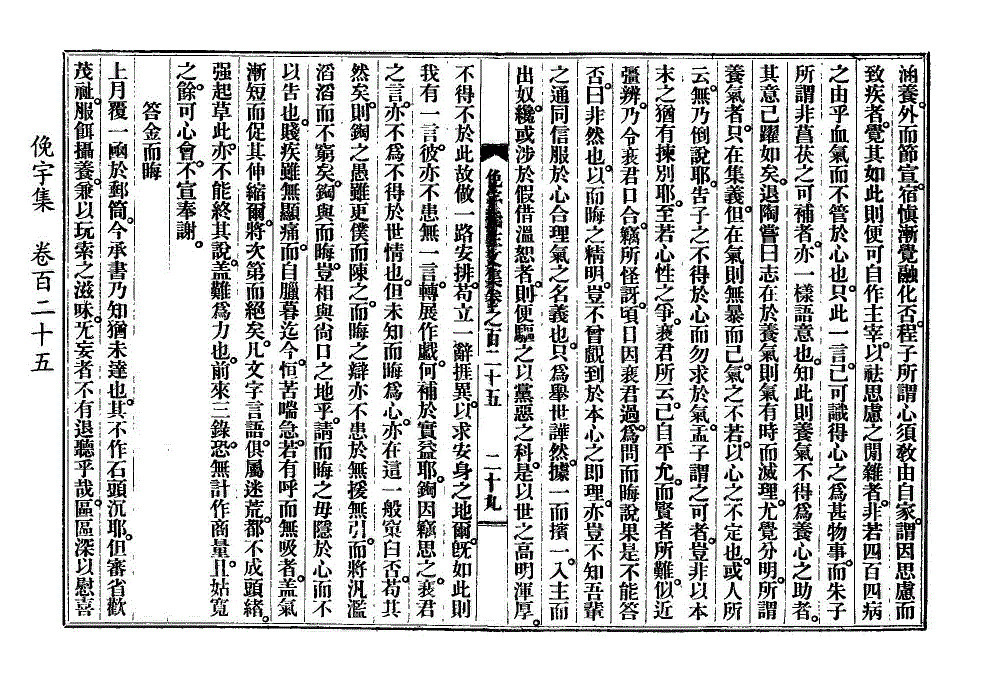 涵养。外而节宣。宿慎渐觉融化否。程子所谓心须教由自家。谓因思虑而致疾者。觉其如此则便可自作主宰。以祛思虑之閒杂者。非若四百四病之由乎血气而不管于心也。只此一言。已可识得心之为甚物事。而朱子所谓非菖茯之可补者。亦一样语意也。知此则养气不得为养心之助者。其意已跃如矣。退陶尝曰志在于养气则气有时而灭理。尤觉分明。所谓养气者。只在集义。但在气则无暴而已。气之不若。以心之不定也。或人所云。无乃倒说耶。告子之不得于心而勿求于气。孟子谓之可者。岂非以本末之犹有拣别耶。至若心性之争。裴君所云。已自平允。而贤者所难。似近彊辨。乃令裴君口合。窃所怪讶。顷日因裴君过。为问而晦说果是不能答否。曰非然也。以而晦之精明。岂不曾觑到于本心之即理。亦岂不知吾辈之通同信服于心合理气之名义也。只为举世哗然。据一而摈一。入主而出奴。才或涉于假借温恕者。则便驱之以党恶之科。是以世之高明浑厚。不得不于此故做一路安排。苟立一辞挨异。以求安身之地尔。既如此则我有一言。彼亦不患无一言。转展作戏。何补于实益耶。鋾因窃思之。裴君之言。亦不为不得于世情也。但未知而晦为心。亦在这一般窠臼否。苟其然矣。则鋾之愚虽更仆而陈之。而晦之辩亦不患于无援无引。而将汎滥滔滔而不穷矣。鋾与而晦。岂相与尚口之地乎。请而晦之毋隐于心而不以告也。贱疾虽无显痛。而自腊暮迄今。恒苦喘急。若有呼而无吸者。盖气渐短而促其伸缩尔。将次第而绝矣。凡文字言语。俱属迷荒。都不成头绪。强起草此。亦不能终其说。盖难为力也。前来三录。恐无计作商量。且姑宽之。馀可心会。不宣奉谢。
涵养。外而节宣。宿慎渐觉融化否。程子所谓心须教由自家。谓因思虑而致疾者。觉其如此则便可自作主宰。以祛思虑之閒杂者。非若四百四病之由乎血气而不管于心也。只此一言。已可识得心之为甚物事。而朱子所谓非菖茯之可补者。亦一样语意也。知此则养气不得为养心之助者。其意已跃如矣。退陶尝曰志在于养气则气有时而灭理。尤觉分明。所谓养气者。只在集义。但在气则无暴而已。气之不若。以心之不定也。或人所云。无乃倒说耶。告子之不得于心而勿求于气。孟子谓之可者。岂非以本末之犹有拣别耶。至若心性之争。裴君所云。已自平允。而贤者所难。似近彊辨。乃令裴君口合。窃所怪讶。顷日因裴君过。为问而晦说果是不能答否。曰非然也。以而晦之精明。岂不曾觑到于本心之即理。亦岂不知吾辈之通同信服于心合理气之名义也。只为举世哗然。据一而摈一。入主而出奴。才或涉于假借温恕者。则便驱之以党恶之科。是以世之高明浑厚。不得不于此故做一路安排。苟立一辞挨异。以求安身之地尔。既如此则我有一言。彼亦不患无一言。转展作戏。何补于实益耶。鋾因窃思之。裴君之言。亦不为不得于世情也。但未知而晦为心。亦在这一般窠臼否。苟其然矣。则鋾之愚虽更仆而陈之。而晦之辩亦不患于无援无引。而将汎滥滔滔而不穷矣。鋾与而晦。岂相与尚口之地乎。请而晦之毋隐于心而不以告也。贱疾虽无显痛。而自腊暮迄今。恒苦喘急。若有呼而无吸者。盖气渐短而促其伸缩尔。将次第而绝矣。凡文字言语。俱属迷荒。都不成头绪。强起草此。亦不能终其说。盖难为力也。前来三录。恐无计作商量。且姑宽之。馀可心会。不宣奉谢。答金而晦
上月覆一函于邮筒。今承书乃知犹未达也。其不作石头沉耶。但审省欢茂祉。服饵摄养。兼以玩索之滋味。无妄者不有退听乎哉。区区深以慰喜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二十五 第 3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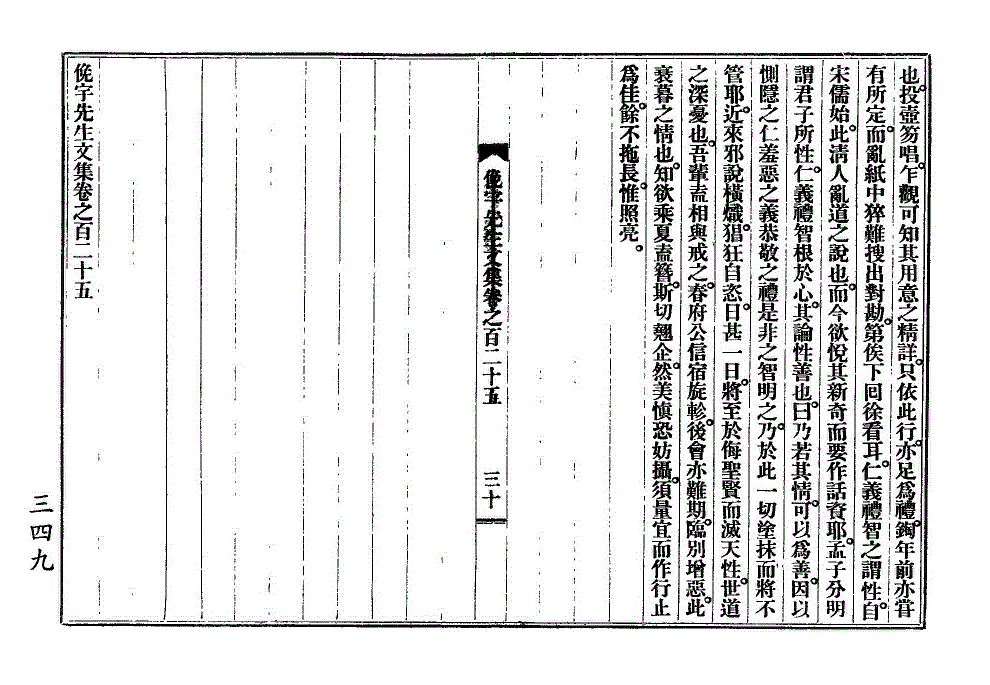 也。投壶笏唱。乍观可知其用意之精详。只依此行。亦足为礼。鋾年前亦尝有所定。而乱纸中猝难搜出对勘。第俟下回徐看耳。仁义礼智之谓性。自宋儒始。此清人乱道之说也。而今欲悦其新奇而要作话资耶。孟子分明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论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可以为善。因以恻隐之仁羞恶之义恭敬之礼是非之智明之。乃于此一切涂抹而将不管耶。近来邪说横炽。猖狂自恣。日甚一日。将至于侮圣贤而灭天性。世道之深忧也。吾辈盍相与戒之。春府公信宿旋轸。后会亦难期。临别增恶。此衰暮之情也。知欲乘夏盍簪。斯切翘企。然美慎恐妨摄。须量宜而作行止为佳。馀不拖长。惟照亮。
也。投壶笏唱。乍观可知其用意之精详。只依此行。亦足为礼。鋾年前亦尝有所定。而乱纸中猝难搜出对勘。第俟下回徐看耳。仁义礼智之谓性。自宋儒始。此清人乱道之说也。而今欲悦其新奇而要作话资耶。孟子分明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论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可以为善。因以恻隐之仁羞恶之义恭敬之礼是非之智明之。乃于此一切涂抹而将不管耶。近来邪说横炽。猖狂自恣。日甚一日。将至于侮圣贤而灭天性。世道之深忧也。吾辈盍相与戒之。春府公信宿旋轸。后会亦难期。临别增恶。此衰暮之情也。知欲乘夏盍簪。斯切翘企。然美慎恐妨摄。须量宜而作行止为佳。馀不拖长。惟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