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书
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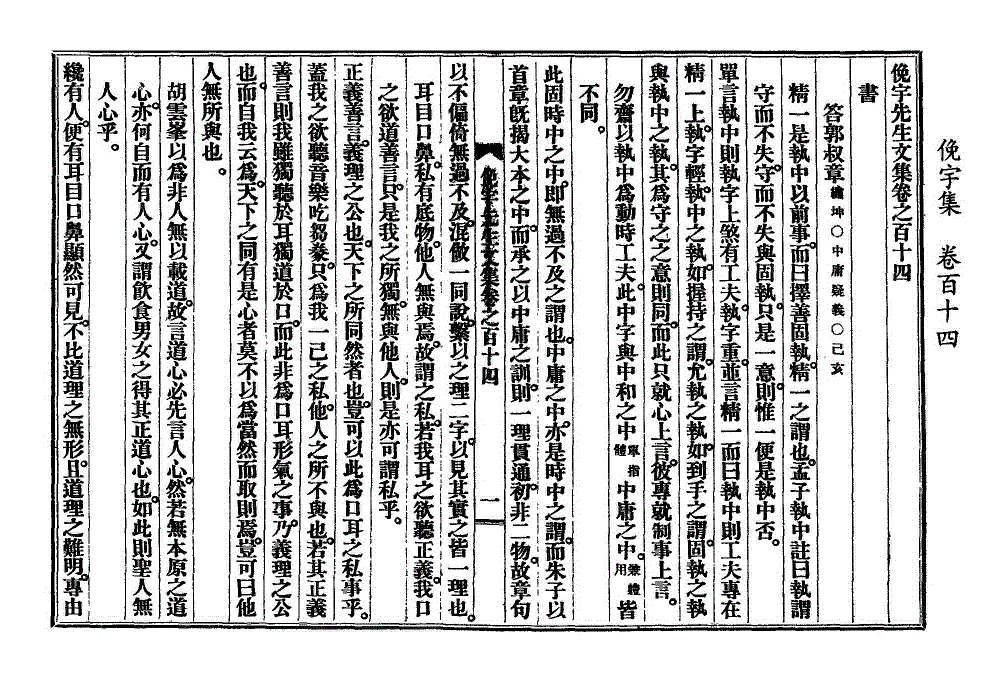 答郭叔章(绣坤○中庸疑义○己亥)
答郭叔章(绣坤○中庸疑义○己亥)精一是执中以前事。而曰择善固执。精一之谓也。孟子执中注曰执谓守而不失。守而不失与固执。只是一意。则惟一便是执中否。
单言执中则执字上煞有工夫。执字重。并言精一而曰执中则工夫专在精一上。执字轻。执中之执。如握持之谓。允执之执。如到手之谓。固执之执与执中之执。其为守之之意则同。而此只就心上言。彼专就制事上言。
勿斋以执中为动时工夫。此中字与中和之中(单指体)中庸之中。(兼体用)皆不同。
此固时中之中。即无过不及之谓也。中庸之中。亦是时中之谓。而朱子以首章既揭大本之中。而承之以中庸之训。则一理贯通。初非二物。故章句以不偏倚无过不及。混做一同说。系以之理二字。以见其实之皆一理也。
耳目口鼻。私有底物。他人无与焉。故谓之私。若我耳之欲听正义。我口之欲道善言。只是我之所独。无与他人。则是亦可谓私乎。
正义善言。义理之公也。天下之所同然者也。岂可以此为口耳之私事乎。盖我之欲听音乐吃刍豢。只为我一己之私。他人之所不与也。若其正义善言则我虽独听于耳独道于口。而此非为口耳形气之事。乃义理之公也。而自我云为。天下之同有是心者莫不以为当然而取则焉。岂可曰他人无所与也。
胡云峰以为非人无以载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然若无本原之道心。亦何自而有人心。又谓饮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如此则圣人无人心乎。
才有人。便有耳目口鼻显然可见。不比道理之无形。且道理之难明。专由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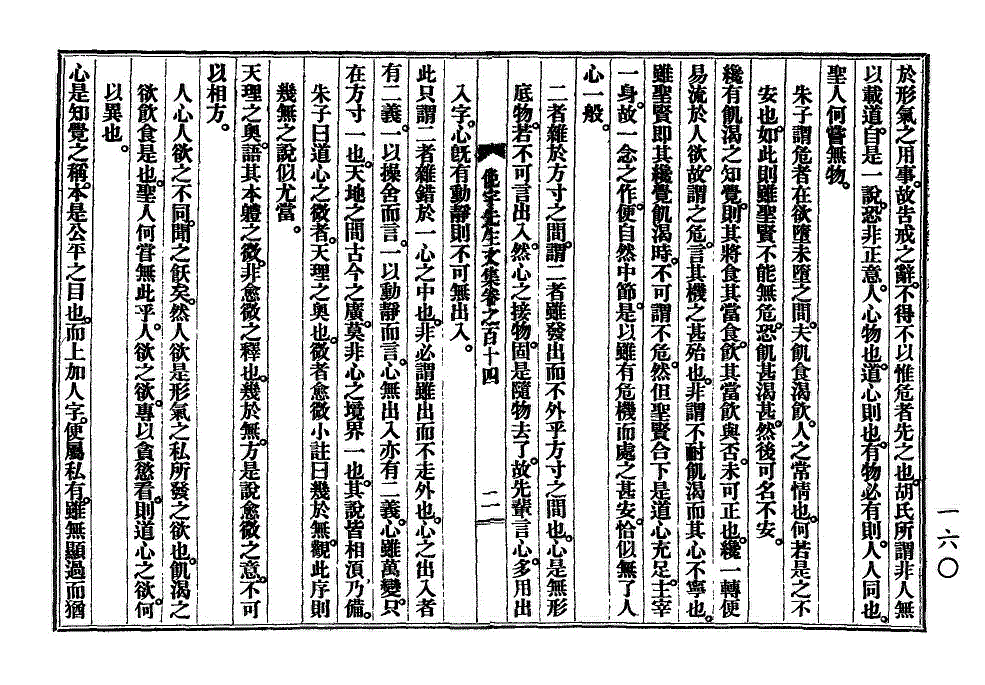 于形气之用事。故告戒之辞。不得不以惟危者先之也。胡氏所谓非人无以载道。自是一说。恐非正意。人心物也。道心则也。有物必有则。人人同也。圣人何尝无物。
于形气之用事。故告戒之辞。不得不以惟危者先之也。胡氏所谓非人无以载道。自是一说。恐非正意。人心物也。道心则也。有物必有则。人人同也。圣人何尝无物。朱子谓危者在欲堕未堕之间。夫饥食渴饮。人之常情也。何若是之不安也。如此则虽圣贤不能无危。恐饥甚渴甚。然后可名不安。
才有饥渴之知觉。则其将食其当食。饮其当饮与否。未可正也。才一转便易流于人欲。故谓之危。言其机之甚殆也。非谓不耐饥渴而其心不宁也。虽圣贤即其才觉饥渴时。不可谓不危。然但圣贤合下是道心充足。主宰一身。故一念之作。便自然中节。是以虽有危机而处之甚安。恰似无了人心一般。
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谓二者虽发出而不外乎方寸之间也。心是无形底物。若不可言出入。然心之接物。固是随物去了。故先辈言心。多用出入字。心既有动静则不可无出入。
此只谓二者杂错于一心之中也。非必谓虽出而不走外也。心之出入者有二义。一以操舍而言。一以动静而言。心无出入亦有二义。心虽万变。只在方寸一也。天地之间古今之广。莫非心之境界一也。其说皆相须乃备。
朱子曰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微者愈微小注曰几于无。观此序则几无之说似尤当。
天理之奥。语其本体之微。非愈微之释也。几于无。方是说愈微之意。不可以相方。
人心人欲之不同。闻之饫矣。然人欲是形气之私所发之欲也。饥渴之欲饮食是也。圣人何尝无此乎。人欲之欲。专以贪欲看。则道心之欲。何以异也。
心是知觉之称。本是公平之目也。而上加人字。便属私有。虽无显过而犹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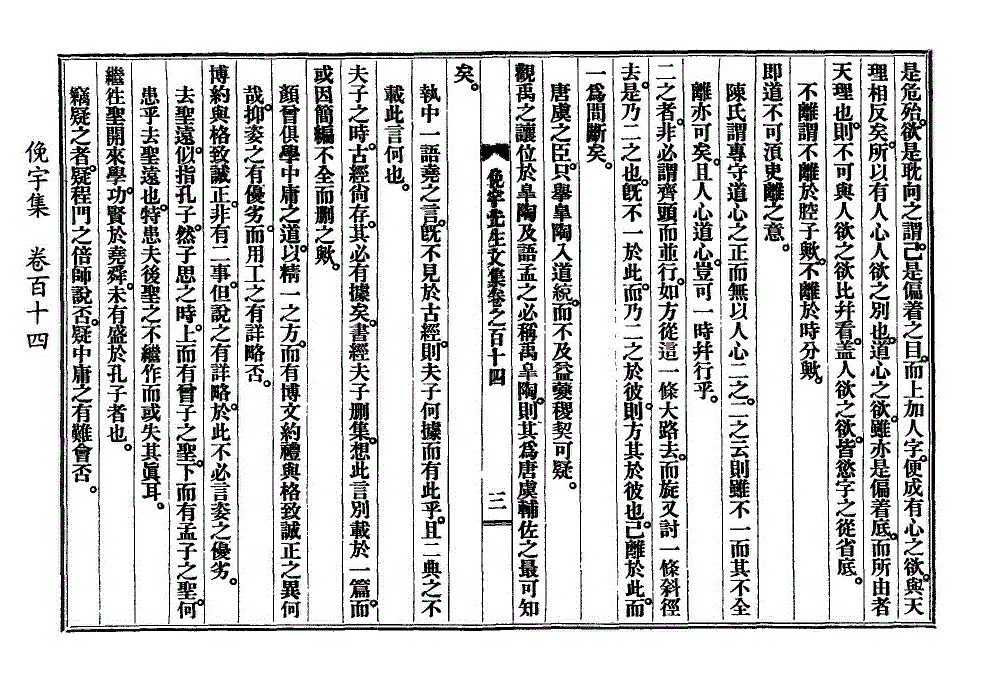 是危殆。欲是耽向之谓。已是偏着之目。而上加人字。便成有心之欲。与天理相反矣。所以有人心人欲之别也。道心之欲。虽亦是偏着底。而所由者天理也。则不可与人欲之欲比并看。盖人欲之欲。皆欲字之从省底。
是危殆。欲是耽向之谓。已是偏着之目。而上加人字。便成有心之欲。与天理相反矣。所以有人心人欲之别也。道心之欲。虽亦是偏着底。而所由者天理也。则不可与人欲之欲比并看。盖人欲之欲。皆欲字之从省底。不离谓不离于腔子欤。不离于时分欤。
即道不可须臾离之意。
陈氏谓专守道心之正而无以人心二之。二之云则虽不一而其不全离亦可矣。且人心道心。岂可一时并行乎。
二之者。非必谓齐头而并行。如方从这一条大路去。而旋又讨一条斜径去。是乃二之也。既不一于此。而乃二之于彼。则方其于彼也。已离于此。而一为间断矣。
唐虞之臣。只举皋陶入道统。而不及益夔稷契可疑。
观禹之让位于皋陶及语孟之必称禹皋陶。则其为唐虞辅佐之最可知矣。
执中一语尧之言。既不见于古经。则夫子何据而有此乎。且二典之不载此言何也。
夫子之时。古经尚存。其必有据矣。书经夫子删集。想此言别载于一篇。而或因简编不全而删之欤。
颜曾俱学中庸之道。以精一之方。而有博文约礼与格致诚正之异何哉。抑姿之有优劣。而用工之有详略否。
博约与格致诚正。非有二事。但说之有详略。于此不必言姿之优劣。
去圣远。似指孔子。然子思之时。上而有曾子之圣。下而有孟子之圣。何患乎去圣远也。特患夫后圣之不继作而或失其真耳。
继往圣开来学。功贤于尧舜。未有盛于孔子者也。
窃疑之者。疑程门之倍师说否。疑中庸之有难会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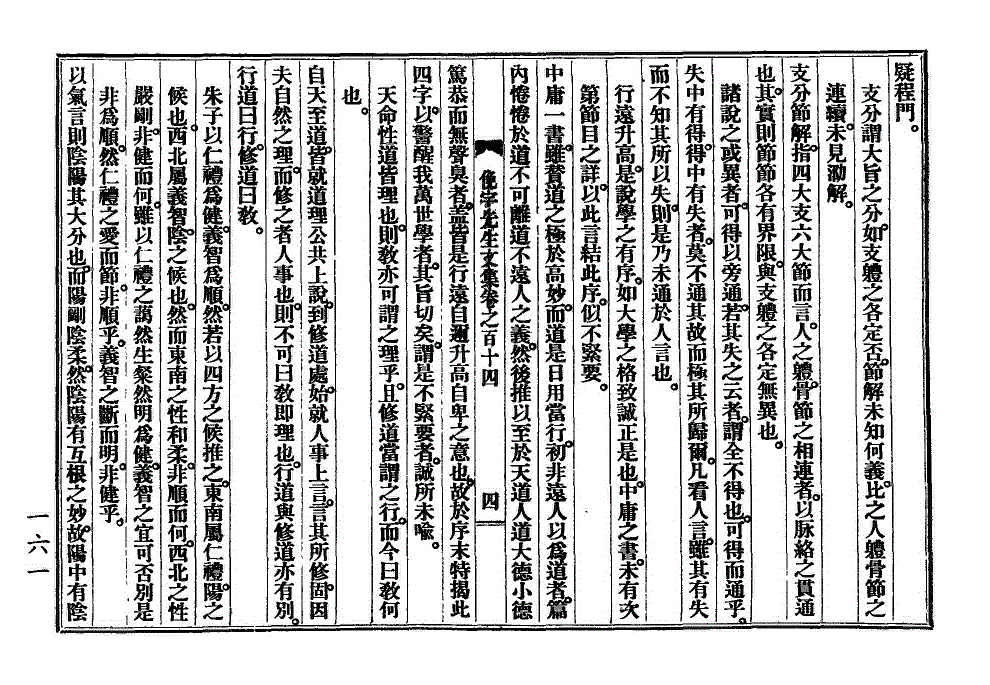 疑程门。
疑程门。支分谓大旨之分。如支体之各定否。节解未知何义。比之人体骨节之连续。未见泐解。
支分节解。指四大支六大节而言。人之体。骨节之相连者。以脉络之贯通也。其实则节节各有界限。与支体之各定无异也。
诸说之或异者。可得以旁通。若其失之云者。谓全不得也。可得而通乎。
失中有得。得中有失者。莫不通其故而极其所归尔。凡看人言。虽其有失而不知其所以失。则是乃未通于人言也。
行远升高。是说学之有序。如大学之格致诚正是也。中庸之书。未有次第节目之详。以此言结此序。似不紧要。
中庸一书。虽赞道之极于高妙。而道是日用当行。初非远人以为道者。篇内惓惓于道不可离道不远人之义。然后推以至于天道人道大德小德笃恭而无声臭者。盖皆是行远自迩升高自卑之意也。故于序末特揭此四字。以警醒我万世学者。其旨切矣。谓是不紧要者。诚所未喻。
天命性道皆理也。则教亦可谓之理乎。且修道当谓之行。而今曰教何也。
自天至道。皆就道理公共上说。到修道处。始就人事上言。言其所修。固因夫自然之理。而修之者人事也。则不可曰教即理也。行道与修道亦有别。行道曰行。修道曰教。
朱子以仁礼为健。义智为顺。然若以四方之候推之。东南属仁礼。阳之候也。西北属义智。阴之候也。然而东南之性和柔。非顺而何。西北之性严刚。非健而何。虽以仁礼之蔼然生粲然明为健。义智之宜可否别是非为顺。然仁礼之爱而节。非顺乎。义智之断而明。非健乎。
以气言则阴阳其大分也。而阳刚阴柔。然阴阳有互根之妙。故阳中有阴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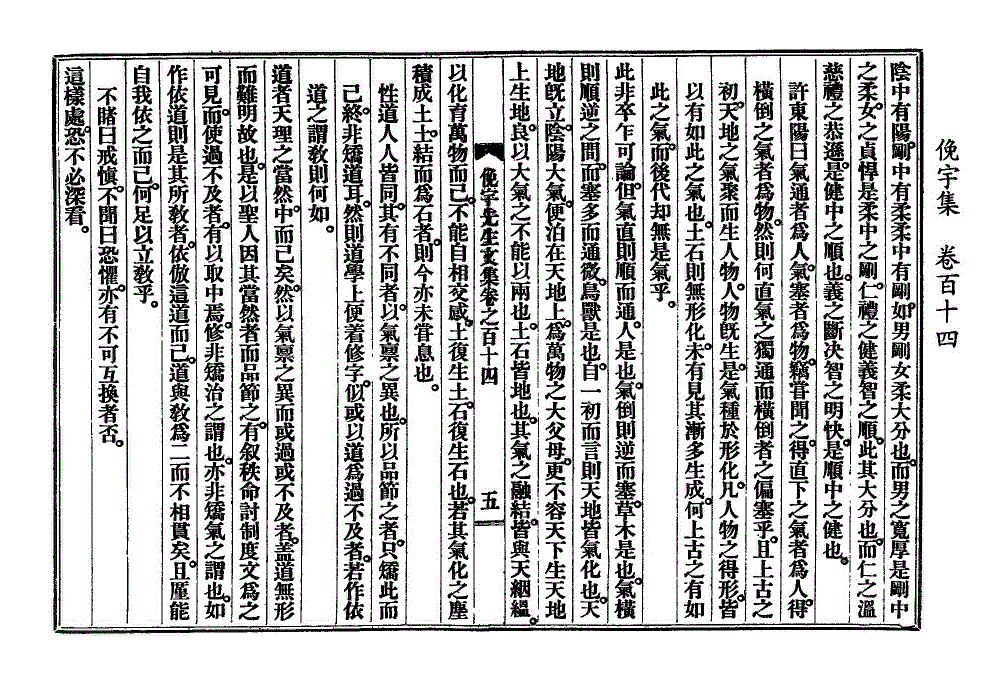 阴中有阳。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如男刚女柔大分也。而男之宽厚是刚中之柔。女之贞悍是柔中之刚。仁礼之健义智之顺。此其大分也。而仁之温慈礼之恭逊。是健中之顺也。义之断决智之明快。是顺中之健也。
阴中有阳。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如男刚女柔大分也。而男之宽厚是刚中之柔。女之贞悍是柔中之刚。仁礼之健义智之顺。此其大分也。而仁之温慈礼之恭逊。是健中之顺也。义之断决智之明快。是顺中之健也。许东阳曰气通者为人。气塞者为物。窃尝闻之。得直下之气者为人。得横倒之气者为物。然则何直气之独通而横倒者之偏塞乎。且上古之初。天地之气聚而生人物。人物既生。是气种于形化。凡人物之得形。皆以有如此之气也。土石则无形化。未有见其渐多生成。何上古之有如此之气。而后代却无是气乎。
此非卒乍可论。但气直则顺而通。人是也。气倒则逆而塞。草木是也。气横则顺逆之间。而塞多而通微。鸟兽是也。自一初而言则天地皆气化也。天地既立。阴阳大气。便泊在天地上。为万物之大父母。更不容天下生天地上生地。良以大气之不能以两也。土石皆地也。其气之融结。皆与天絪缊。以化育万物而已。不能自相交感。土复生土。石复生石也。若其气化之尘积成土。土结而为石者。则今亦未尝息也。
性道人人皆同。其有不同者。以气禀之异也。所以品节之者。只矫此而已。终非矫道耳。然则道学上便着修字。似或以道为过不及者。若作依道之谓教则何如。
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然以气禀之异而或过或不及者。盖道无形而难明故也。是以圣人因其当然者而品节之。有叙秩命讨制度文为之可见。而使过不及者。有以取中焉。修非矫治之谓也。亦非矫气之谓也。如作依道则是其所教者。依仿这道而已。道与教为二而不相贯矣。且廑能自我依之而已。何足以立教乎。
不睹曰戒慎。不闻曰恐惧。亦有不可互换者否。
这样处。恐不必深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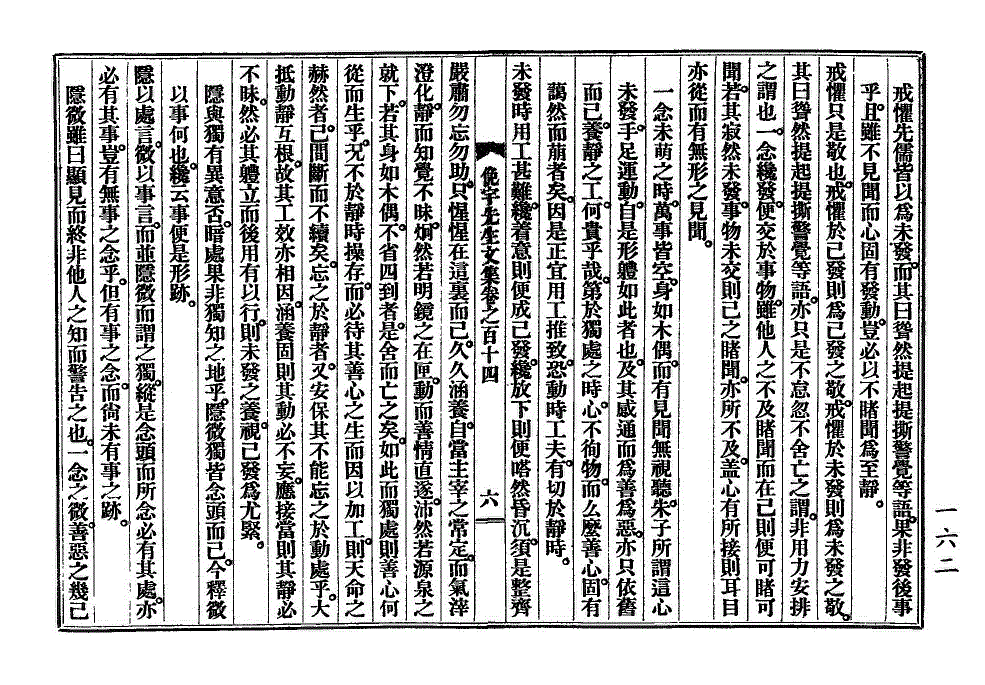 戒惧先儒皆以为未发。而其曰耸然提起提撕警觉等语。果非发后事乎。且虽不见闻而心固有发动。岂必以不睹闻为至静。
戒惧先儒皆以为未发。而其曰耸然提起提撕警觉等语。果非发后事乎。且虽不见闻而心固有发动。岂必以不睹闻为至静。戒惧只是敬也。戒惧于已发则为已发之敬。戒惧于未发则为未发之敬。其曰耸然提起提撕警觉等语。亦只是不怠忽不舍亡之谓。非用力安排之谓也。一念才发。便交于事物。虽他人之不及睹闻而在己则便可睹可闻。若其寂然未发。事物未交则己之睹闻。亦所不及。盖心有所接则耳目亦从而有无形之见闻。
一念未萌之时。万事皆空。身如木偶。而有见闻无视听。朱子所谓这心未发。手足运动。自是形体如此者也。及其感通而为善为恶。亦只依旧而已。养静之工。何贵乎哉。第于独处之时。心不徇物。而幺么善心。固有蔼然而萌者矣。因是正宜用工推致。恐动时工夫。有切于静时。
未发时用工甚难。才着意则便成已发。才放下则便㗳然昏沉。须是整齐严肃勿忘勿助。只惺惺在这里而已。久久涵养。自当主宰之常定。而气滓澄化。静而知觉不昧。炯然若明镜之在匣。动而善情直遂。沛然若源泉之就下。若其身如木偶。不省四到者。是舍而亡之矣。如此而独处则善心何从而生乎。况不于静时操存。而必待其善心之生而因以加工。则天命之赫然者。已间断而不续矣。忘之于静者。又安保其不能忘之于动处乎。大抵动静互根。故其工效亦相因。涵养固则其动必不妄。应接当则其静必不昧。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未发之养。视已发为尤紧。
隐与独有异意否。暗处果非独知之地乎。隐微独皆念头而已。今释微以事何也。才云事便是形迹。
隐以处言。微以事言。而并隐微而谓之独。纵是念头而所念必有其处。亦必有其事。岂有无事之念乎。但有事之念。而尚未有事之迹。
隐微虽曰显见而终非他人之知而警告之也。一念之微。善恶之几已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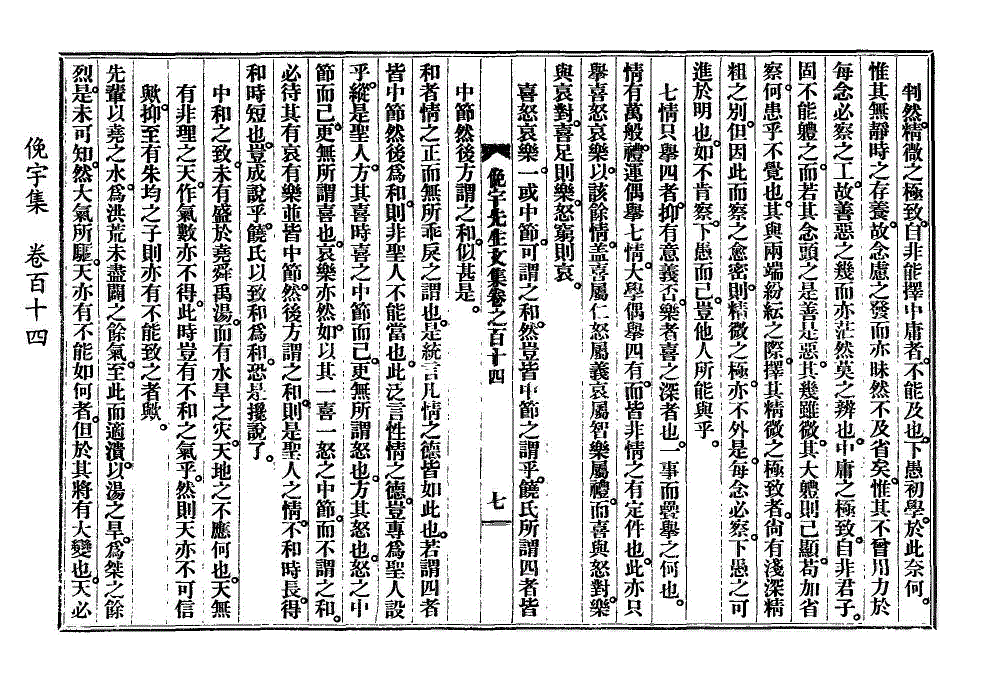 判然。精微之极致。自非能择中庸者。不能及也。下愚初学。于此奈何。
判然。精微之极致。自非能择中庸者。不能及也。下愚初学。于此奈何。惟其无静时之存养。故念虑之发而亦昧然不及省矣。惟其不曾用力于每念必察之工。故善恶之几而亦茫然莫之辨也。中庸之极致。自非君子。固不能体之。而若其念头之是善是恶。其几虽微。其大体则已显。苟加省察。何患乎不觉也。其与两端纷纭之际。择其精微之极致者。尚有浅深精粗之别。但因此而察之愈密。则精微之极。亦不外是。每念必察。下愚之可进于明也。如不肯察。下愚而已。岂他人所能与乎。
七情只举四者。抑有意义否。乐者喜之深者也。一事而叠举之何也。
情有万般。礼运偶举七情。大学偶举四有。而皆非情之有定件也。此亦只举喜怒哀乐。以该馀情。盖喜属仁怒属义哀属智乐属礼。而喜与怒对。乐与哀对。喜足则乐。怒穷则哀。
喜怒哀乐。一或中节。可谓之和。然岂皆中节之谓乎。饶氏所谓四者皆中节然后方谓之和。似甚是。
和者情之正而无所乖戾之谓也。是统言凡情之德皆如此也。若谓四者皆中节然后为和。则非圣人不能当也。此泛言性情之德。岂专为圣人设乎。纵是圣人。方其喜时喜之中节而已。更无所谓怒也。方其怒也。怒之中节而已。更无所谓喜也。哀乐亦然。如以其一喜一怒之中节。而不谓之和。必待其有哀有乐并皆中节。然后方谓之和。则是圣人之情。不和时长。得和时短也。岂成说乎。饶氏以致和为和。恐是搀说了。
中和之致。未有盛于尧舜禹汤。而有水旱之灾。天地之不应何也。天无有非理之天。作气数亦不得。此时岂有不和之气乎。然则天亦不可信欤。抑至有朱均之子则亦有不能致之者欤。
先辈以尧之水。为洪荒未尽辟之馀气。至此而适溃。以汤之旱。为桀之馀烈。是未可知。然大气所驱。天亦有不能如何者。但于其将有大变也。天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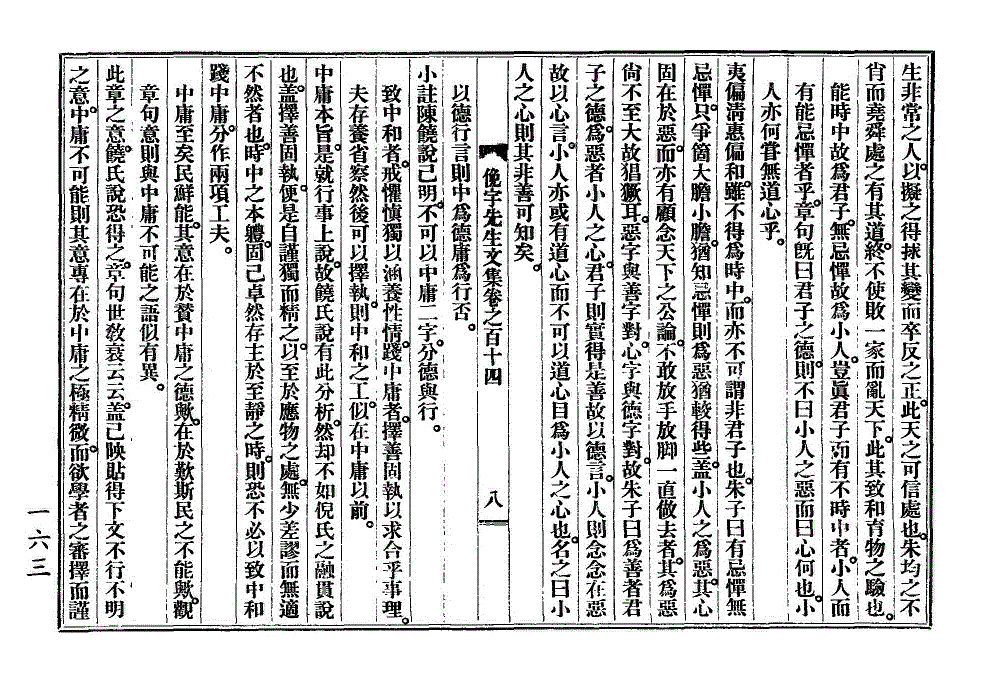 生非常之人。以拟之得救其变而卒反之正。此天之可信处也。朱均之不肖而尧舜处之有其道。终不使败一家而乱天下。此其致和育物之验也。
生非常之人。以拟之得救其变而卒反之正。此天之可信处也。朱均之不肖而尧舜处之有其道。终不使败一家而乱天下。此其致和育物之验也。能时中故为君子。无忌惮故为小人。岂真君子而有不时中者。小人而有能忌惮者乎。章句既曰君子之德。则不曰小人之恶而曰心何也。小人亦何尝无道心乎。
夷偏清惠偏和。虽不得为时中。而亦不可谓非君子也。朱子曰有忌惮无忌惮。只争个大胆小胆。犹知忌惮则为恶犹较得些。盖小人之为恶。其心固在于恶。而亦有顾念天下之公论。不敢放手放脚一直做去者。其为恶尚不至大故猖獗耳。恶字与善字对。心字与德字对。故朱子曰为善者君子之德。为恶者小人之心。君子则实得是善故以德言。小人则念念在恶故以心言。小人亦或有道心而不可以道心目为小人之心也。名之曰小人之心则其非善可知矣。
以德行言则中为德庸为行否。
小注陈饶说已明。不可以中庸二字。分德与行。
致中和者。戒惧慎独以涵养性情。践中庸者。择善固执以求合乎事理。夫存养省察然后可以择执。则中和之工。似在中庸以前。
中庸本旨。是就行事上说。故饶氏说有此分析。然却不如倪氏之融贯说也。盖择善固执。便是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者也。时中之本体。固已卓然存主于至静之时。则恐不必以致中和践中庸。分作两项工夫。
中庸至矣民鲜能。其意在于赞中庸之德欤。在于叹斯民之不能欤。观章句意则与中庸不可能之语似有异。
此章之意。饶氏说恐得之。章句世教衰云云。盖已映贴得下文不行不明之意。中庸不可能则其意专在于中庸之极精微。而欲学者之审择而谨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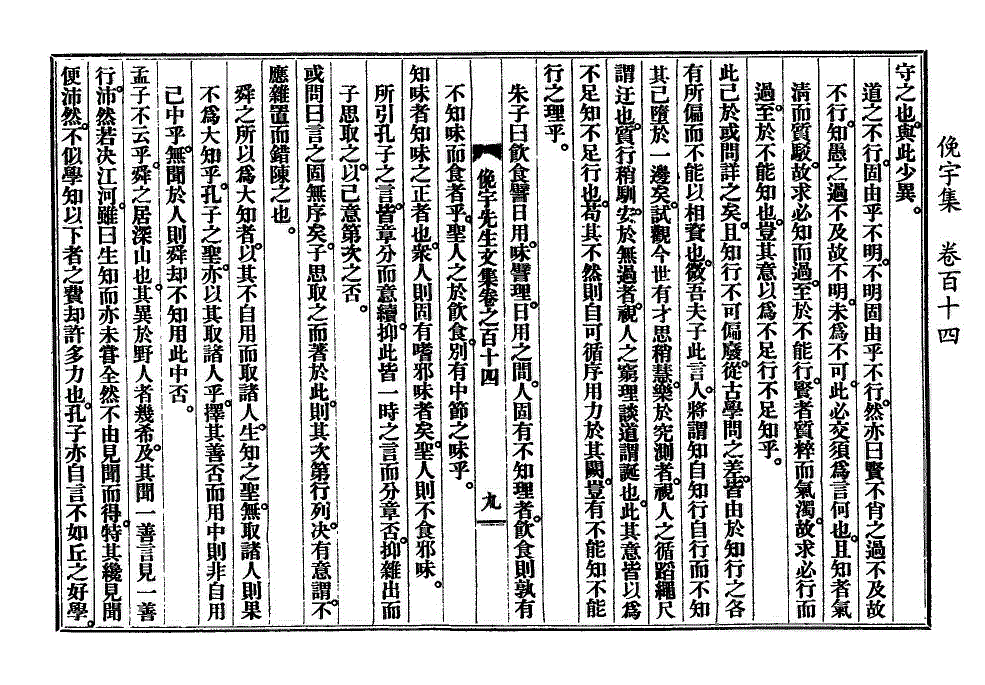 守之也。与此少异。
守之也。与此少异。道之不行。固由乎不明。不明固由乎不行。然亦曰贤不肖之过不及故不行。知愚之过不及故不明。未为不可。此必交须为言何也。且知者气清而质驳。故求必知而过。至于不能行。贤者质粹而气浊。故求必行而过。至于不能知也。岂其意以为不足行不足知乎。
此已于或问详之矣。且知行不可偏废。从古学问之差。皆由于知行之各有所偏而不能以相资也。微吾夫子此言。人将谓知自知行自行而不知其已堕于一边矣。试观今世有才思稍慧。乐于究测者。视人之循蹈绳尺谓迂也。质行稍驯。安于无过者。视人之穷理谈道谓诞也。此其意皆以为不足知不足行也。苟其不然则自可循序用力于其阙。岂有不能知不能行之理乎。
朱子曰饮食譬日用。味譬理。日用之间。人固有不知理者。饮食则孰有不知味而食者乎。圣人之于饮食。别有中节之味乎。
知味者知味之正者也。众人则固有嗜邪味者矣。圣人则不食邪味。
所引孔子之言。皆章分而意续。抑此皆一时之言而分章否。抑杂出而子思取之。以己意第次之否。
或问曰言之固无序矣。子思取之而著于此。则其次第行列。决有意谓。不应杂置而错陈之也。
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生知之圣。无取诸人则果不为大知乎。孔子之圣。亦以其取诸人乎。择其善否而用中则非自用已中乎。无闻于人则舜却不知用此中否。
孟子不云乎。舜之居深山也。其异于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虽曰生知而亦未尝全然不由见闻而得。特其才见闻便沛然。不似学知以下者之费却许多力也。孔子亦自言不如丘之好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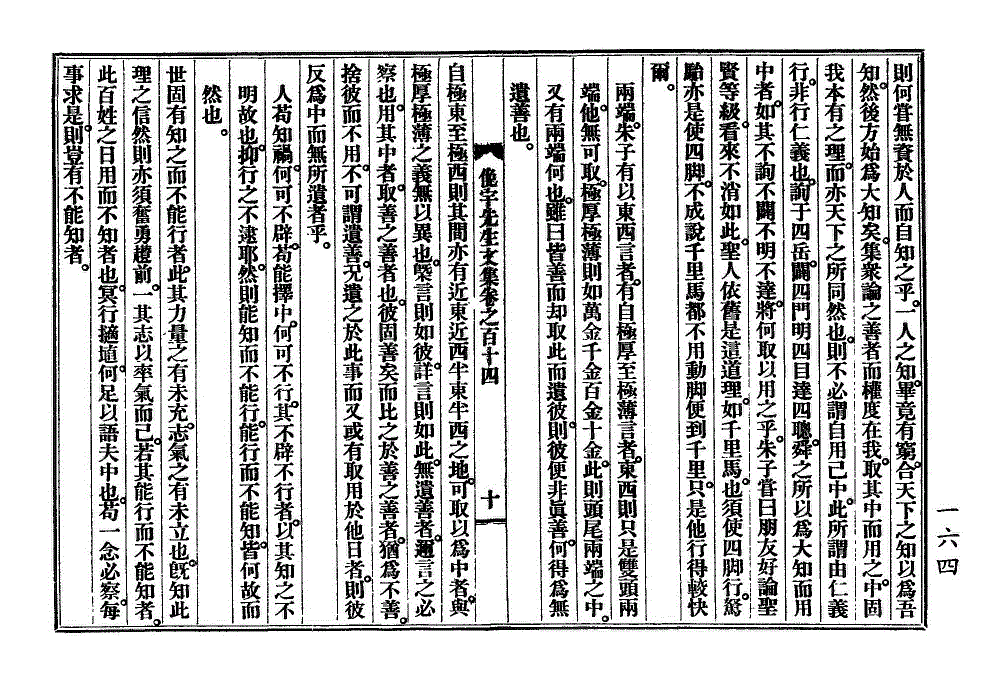 则何尝无资于人而自知之乎。一人之知。毕竟有穷。合天下之知以为吾知。然后方始为大知矣。集众论之善者而权度在我。取其中而用之。中固我本有之理。而亦天下之所同然也。则不必谓自用己中。此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舜之所以为大知而用中者。如其不询不辟不明不达。将何取以用之乎。朱子尝曰朋友好论圣贤等级。看来不消如此。圣人依旧是这道理。如千里马。也须使四脚行。驽骀亦是使四脚。不成说千里马都不用动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较快尔。
则何尝无资于人而自知之乎。一人之知。毕竟有穷。合天下之知以为吾知。然后方始为大知矣。集众论之善者而权度在我。取其中而用之。中固我本有之理。而亦天下之所同然也。则不必谓自用己中。此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舜之所以为大知而用中者。如其不询不辟不明不达。将何取以用之乎。朱子尝曰朋友好论圣贤等级。看来不消如此。圣人依旧是这道理。如千里马。也须使四脚行。驽骀亦是使四脚。不成说千里马都不用动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较快尔。两端。朱子有以东西言者。有自极厚至极薄言者。东西则只是双头两端。他无可取。极厚极薄则如万金千金百金十金。此则头尾两端之中。又有两端何也。虽曰皆善而却取此而遗彼。则彼便非真善。何得为无遗善也。
自极东至极西则其间亦有近东近西半东半西之地。可取以为中者。与极厚极薄之义无以异也。槩言则如彼。详言则如此。无遗善者。迩言之必察也。用其中者。取善之善者也。彼固善矣而比之于善之善者。犹为不善。舍彼而不用。不可谓遗善。况遗之于此事而又或有取用于他日者。则彼反为中而无所遗者乎。
人苟知祸。何可不辟。苟能择中。何可不行。其不辟不行者。以其知之不明故也。抑行之不逮耶。然则能知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知。皆何故而然也。
世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此其力量之有未充。志气之有未立也。既知此理之信然则亦须奋勇趱前。一其志以率气而已。若其能行而不能知者。此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也。冥行擿埴。何足以语夫中也。苟一念必察。每事求是。则岂有不能知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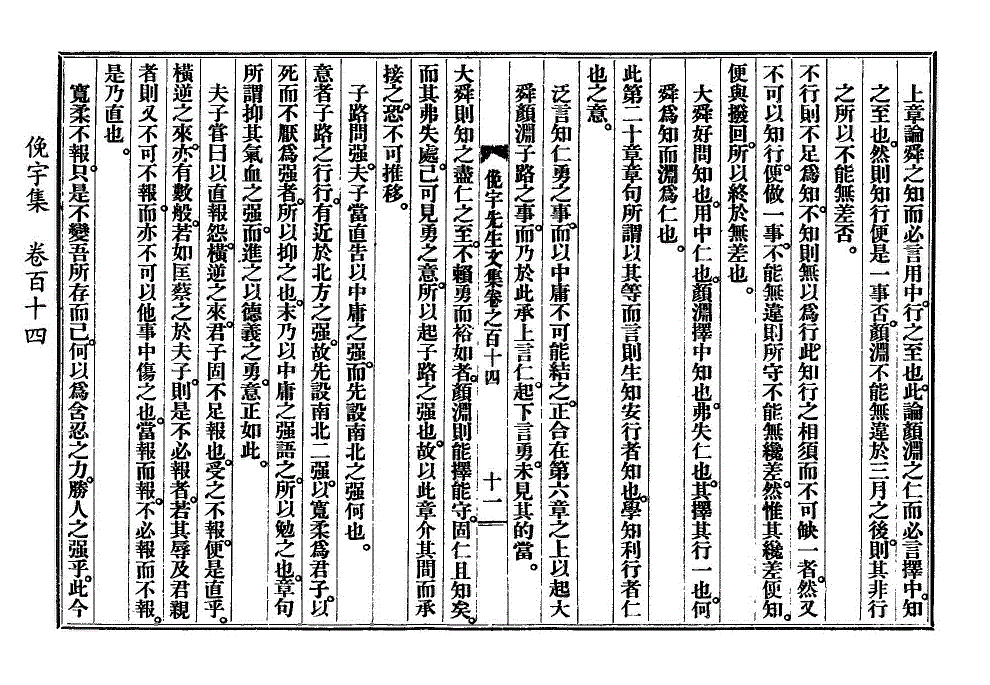 上章论舜之知而必言用中。行之至也。此论颜渊之仁而必言择中。知之至也。然则知行便是一事否。颜渊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则其非行之所以不能无差否。
上章论舜之知而必言用中。行之至也。此论颜渊之仁而必言择中。知之至也。然则知行便是一事否。颜渊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则其非行之所以不能无差否。不行则不足为知。不知则无以为行。此知行之相须而不可缺一者。然又不可以知行。便做一事。不能无违则所守不能无才差。然惟其才差便知。便与拨回。所以终于无差也。
大舜好问知也。用中仁也。颜渊择中知也。弗失仁也。其择其行一也。何舜为知而渊为仁也。
此第二十章章句所谓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之意。
泛言知仁勇之事。而以中庸不可能结之。正合在第六章之上以起大舜颜渊子路之事。而乃于此承上言仁。起下言勇。未见其的当。
大舜则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颜渊则能择能守。固仁且知矣。而其弗失处。已可见勇之意。所以起子路之强也。故以此章介其间而承接之。恐不可推移。
子路问强。夫子当直告以中庸之强。而先设南北之强何也。
意者子路之行行。有近于北方之强。故先设南北二强。以宽柔为君子。以死而不厌为强者。所以抑之也。末乃以中庸之强语之。所以勉之也。章句所谓抑其气血之强。而进之以德义之勇。意正如此。
夫子尝曰以直报怨。横逆之来。君子固不足报也。受之不报。便是直乎。
横逆之来。亦有数般。若如匡蔡之于夫子。则是不必报者。若其辱及君亲者则又不可不报。而亦不可以他事中伤之也。当报而报。不必报而不报。是乃直也。
宽柔不报。只是不变吾所存而已。何以为含忍之力。胜人之强乎。此今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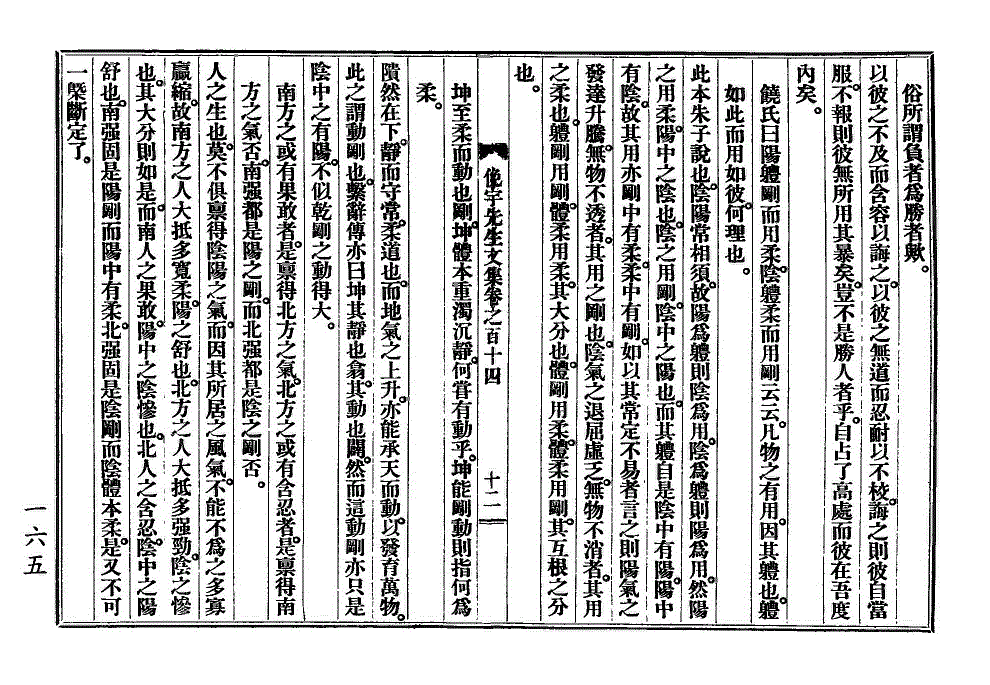 俗所谓负者为胜者欤。
俗所谓负者为胜者欤。以彼之不及而含容以诲之。以彼之无道而忍耐以不校。诲之则彼自当服。不报则彼无所用其暴矣。岂不是胜人者乎。自占了高处而彼在吾度内矣。
饶氏曰阳体刚而用柔。阴体柔而用刚云云。凡物之有用。因其体也。体如此而用如彼。何理也。
此本朱子说也。阴阳常相须。故阳为体则阴为用。阴为体则阳为用。然阳之用柔。阳中之阴也。阴之用刚。阴中之阳也。而其体自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其用亦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如以其常定不易者言之则阳气之发达升腾。无物不透者。其用之刚也。阴气之退屈虚乏。无物不消者。其用之柔也。体刚用刚。体柔用柔。其大分也。体刚用柔。体柔用刚。其互根之分也。
坤至柔而动也刚。坤体本重浊沉静。何尝有动乎。坤能刚动则指何为柔。
隤然在下。静而守常。柔道也。而地气之上升。亦能承天而动。以发育万物。此之谓动刚也。系辞传亦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然而这动刚亦只是阴中之有阳。不似乾刚之动得大。
南方之或有果敢者。是禀得北方之气。北方之或有含忍者。是禀得南方之气否。南强都是阳之刚。而北强都是阴之刚否。
人之生也。莫不俱禀得阴阳之气。而因其所居之风气。不能不为之多寡赢缩。故南方之人大抵多宽柔。阳之舒也。北方之人大抵多强劲。阴之惨也。其大分则如是。而南人之果敢。阳中之阴惨也。北人之含忍。阴中之阳舒也。南强固是阳刚而阳中有柔。北强固是阴刚而阴体本柔。是又不可一槩断定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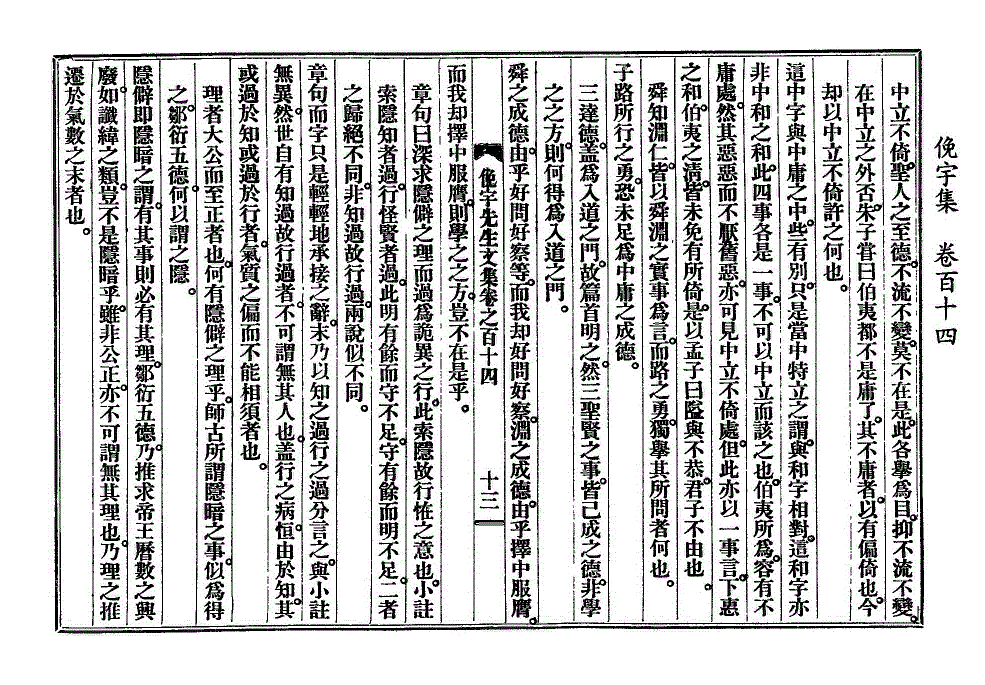 中立不倚。圣人之至德。不流不变。莫不在是。此各举为目。抑不流不变。在中立之外否。朱子尝曰伯夷都不是庸了。其不庸者。以有偏倚也。今却以中立不倚许之何也。
中立不倚。圣人之至德。不流不变。莫不在是。此各举为目。抑不流不变。在中立之外否。朱子尝曰伯夷都不是庸了。其不庸者。以有偏倚也。今却以中立不倚许之何也。这中字与中庸之中。些有别。只是当中特立之谓。与和字相对。这和字亦非中和之和。此四事各是一事。不可以中立而该之也。伯夷所为。容有不庸处。然其恶恶而不厌旧恶。亦可见中立不倚处。但此亦以一事言。下惠之和。伯夷之清。皆未免有所倚。是以孟子曰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舜知渊仁。皆以舜渊之实事为言。而路之勇。独举其所问者何也。
子路所行之勇。恐未足为中庸之成德。
三达德。盖为入道之门。故篇首明之。然三圣贤之事。皆已成之德。非学之之方。则何得为入道之门。
舜之成德。由乎好问好察等。而我却好问好察。渊之成德。由乎择中服膺。而我却择中服膺。则学之之方。岂不在是乎。
章句曰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此索隐故行怪之意也。小注索隐知者过。行怪贤者过。此明有馀而守不足。守有馀而明不足。二者之归绝不同。非知过故行过。两说似不同。
章句而字只是轻轻地承接之辞。末乃以知之过行之过分言之。与小注无异。然世自有知过故行过者。不可谓无其人也。盖行之病。恒由于知。其或过于知或过于行者。气质之偏而不能相须者也。
理者大公而至正者也。何有隐僻之理乎。师古所谓隐暗之事。似为得之。邹衍五德。何以谓之隐。
隐僻即隐暗之谓。有其事则必有其理。邹衍五德。乃推求帝王历数之兴废。如谶纬之类。岂不是隐暗乎。虽非公正。亦不可谓无其理也。乃理之推迁于气数之末者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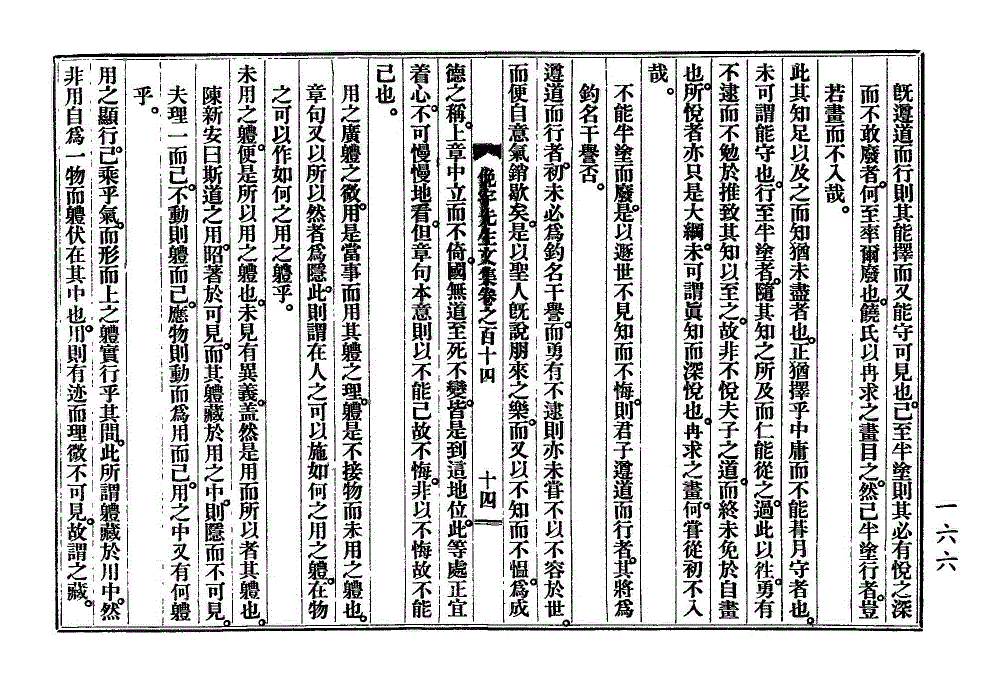 既遵道而行则其能择而又能守可见也。已至半涂则其必有悦之深而不敢废者。何至率尔废也。饶氏以冉求之画目之。然已半涂行者。岂若画而不入哉。
既遵道而行则其能择而又能守可见也。已至半涂则其必有悦之深而不敢废者。何至率尔废也。饶氏以冉求之画目之。然已半涂行者。岂若画而不入哉。此其知足以及之而知犹未尽者也。正犹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也。未可谓能守也。行至半涂者。随其知之所及而仁能从之。过此以往。勇有不逮而不勉于推致其知以至之。故非不悦夫子之道。而终未免于自画也。所悦者亦只是大纲。未可谓真知而深悦也。冉求之画。何尝从初不入哉。
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则君子遵道而行者。其将为钓名干誉否。
遵道而行者。初未必为钓名干誉。而勇有不逮则亦未尝不以不容于世。而便自意气销歇矣。是以圣人既说朋来之乐。而又以不知而不愠。为成德之称。上章中立而不倚。国无道至死不变。皆是到这地位。此等处正宜着心。不可慢慢地看。但章句本意则以不能已故不悔。非以不悔故不能已也。
用之广体之微。用是当事而用其体之理。体是不接物而未用之体也。章句又以所以然者为隐。此则谓在人之可以施如何之用之体。在物之可以作如何之用之体乎。
未用之体。便是所以用之体也。未见有异义。盖然是用而所以者其体也。
陈新安曰斯道之用。昭著于可见。而其体藏于用之中。则隐而不可见。夫理一而已。不动则体而已。应物则动而为用而已。用之中又有何体乎。
用之显行。已乘乎气。而形而上之体实行乎其间。此所谓体藏于用中。然非用自为一物而体伏在其中也。用则有迹而理微不可见。故谓之藏。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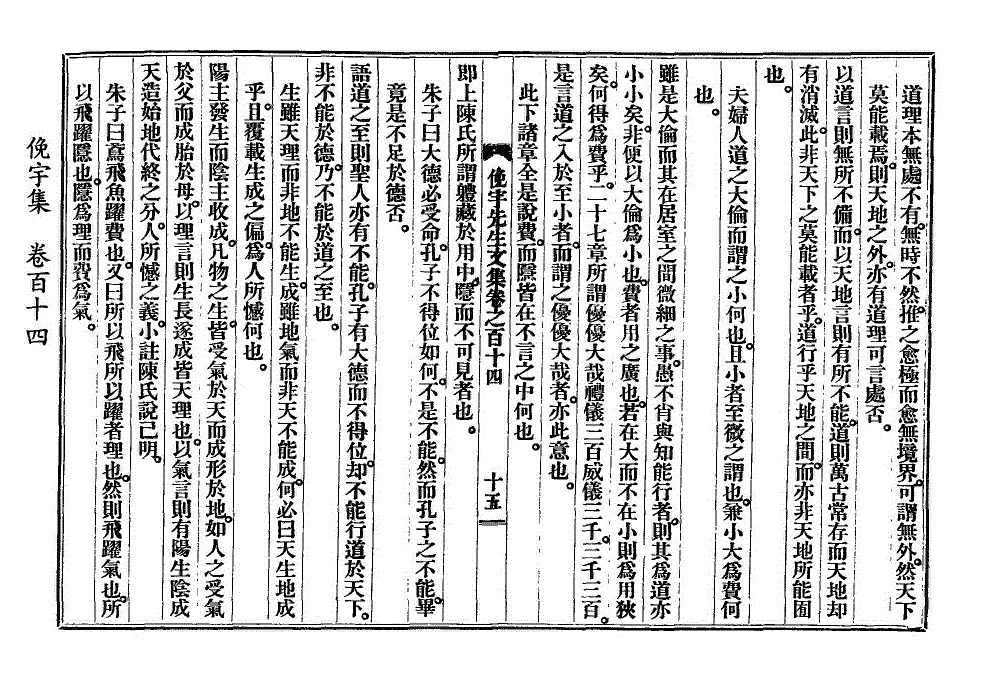 道理本无处不有。无时不然。推之愈极而愈无境界。可谓无外。然天下莫能载焉。则天地之外。亦有道理可言处否。
道理本无处不有。无时不然。推之愈极而愈无境界。可谓无外。然天下莫能载焉。则天地之外。亦有道理可言处否。以道言则无所不备。而以天地言则有所不能。道则万古常存而天地却有消灭。此非天下之莫能载者乎。道行乎天地之间。而亦非天地所能囿也。
夫妇人道之大伦而谓之小何也。且小者至微之谓也。兼小大为费何也。
虽是大伦而其在居室之间微细之事。愚不肖与知能行者。则其为道亦小小矣。非便以大伦为小也。费者用之广也。若在大而不在小则为用狭矣。何得为费乎。二十七章所谓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三千三百。是言道之入于至小者。而谓之优优大哉者。亦此意也。
此下诸章全是说费。而隐皆在不言之中何也。
即上陈氏所谓体藏于用中。隐而不可见者也。
朱子曰大德必受命。孔子不得位如何。不是不能。然而孔子之不能。毕竟是不足于德否。
语道之至则圣人亦有不能。孔子有大德而不得位。却不能行道于天下。非不能于德。乃不能于道之至也。
生虽天理而非地不能生。成虽地气而非天不能成。何必曰天生地成乎。且覆载生成之偏。为人所憾何也。
阳主发生而阴主收成。凡物之生。皆受气于天而成形于地。如人之受气于父而成胎于母。以理言则生长遂成皆天理也。以气言则有阳生阴成天造始地代终之分。人所憾之义。小注陈氏说已明。
朱子曰鸢飞鱼跃费也。又曰所以飞所以跃者理也。然则飞跃气也。所以飞跃隐也。隐为理而费为气。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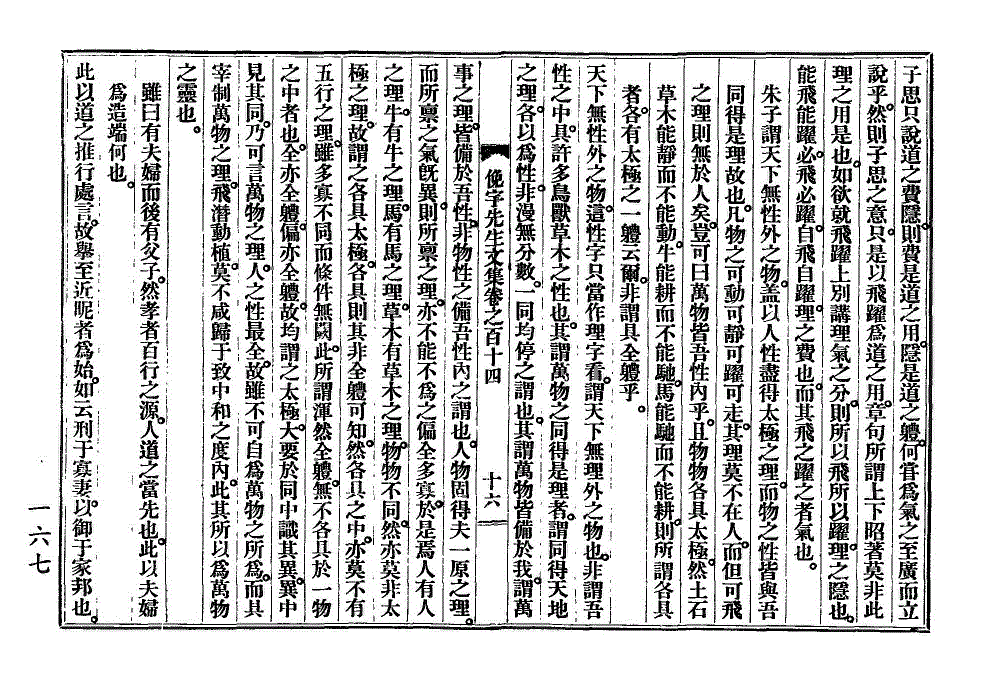 子思只说道之费隐。则费是道之用。隐是道之体。何尝为气之至广而立说乎。然则子思之意。只是以飞跃为道之用。章句所谓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是也。如欲就飞跃上别讲理气之分。则所以飞所以跃。理之隐也。能飞能跃。必飞必跃。自飞自跃。理之费也。而其飞之跃之者气也。
子思只说道之费隐。则费是道之用。隐是道之体。何尝为气之至广而立说乎。然则子思之意。只是以飞跃为道之用。章句所谓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是也。如欲就飞跃上别讲理气之分。则所以飞所以跃。理之隐也。能飞能跃。必飞必跃。自飞自跃。理之费也。而其飞之跃之者气也。朱子谓天下无性外之物。盖以人性尽得太极之理。而物之性皆与吾同得是理故也。凡物之可动可静可跃可走。其理莫不在人。而但可飞之理则无于人矣。岂可曰万物皆吾性内乎。且物物各具太极。然土石草木能静而不能动。牛能耕而不能驰。马能驰而不能耕。则所谓各具者。各有太极之一体云尔。非谓具全体乎。
天下无性外之物。这性字只当作理字看。谓天下无理外之物也。非谓吾性之中。具许多鸟兽草木之性也。其谓万物之同得是理者。谓同得天地之理。各以为性。非漫无分数。一同均停之谓也。其谓万物皆备于我。谓万事之理。皆备于吾性。非物性之备吾性内之谓也。人物固得夫一原之理。而所禀之气既异。则所禀之理。亦不能不为之偏全多寡。于是焉人有人之理。牛有牛之理。马有马之理。草木有草木之理。物物不同。然亦莫非太极之理。故谓之各具太极。各具则其非全体可知。然各具之中。亦莫不有五行之理。虽多寡不同而条件无阙。此所谓浑然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者也。全亦全体。偏亦全体。故均谓之太极。大要于同中识其异。异中见其同。乃可言万物之理。人之性最全。故虽不可自为万物之所为。而具宰制万物之理。飞潜动植。莫不咸归于致中和之度内。此其所以为万物之灵也。
虽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然孝者百行之源。人道之当先也。此以夫妇为造端何也。
此以道之推行处言。故举至近昵者为始。如云形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8H 页
 人道之当行。固莫先于孝亲。而自推行而言则父子之间。慈严两至。慈则易和。严则易敬。夫妇则配耦之密而衽席之亵。密则易狎。亵则易慢。稍失和敬。不能以感服无间。如此则出而应物接人治国经世。亦将诚不足以动人。庄不足以服人。是以圣人以不为二南。谓正墙面而立。君子之造端。其不在是乎。
人道之当行。固莫先于孝亲。而自推行而言则父子之间。慈严两至。慈则易和。严则易敬。夫妇则配耦之密而衽席之亵。密则易狎。亵则易慢。稍失和敬。不能以感服无间。如此则出而应物接人治国经世。亦将诚不足以动人。庄不足以服人。是以圣人以不为二南。谓正墙面而立。君子之造端。其不在是乎。章下以费隐为申明道不可离之意。然费者无物不有之谓也。何以不可离于己乎。
费是道之用。道非吾日用当行者乎。无物不有而日用之接。非物事乎。有物必有则则非天理之在我者乎。朱子尝曰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不可以为道。谚解作不可谓道之意。然为道远人章句。谓高远难行。高远亦道也。岂可不谓之道乎。恐是言人之为道。不由近而务求远则无由为其道也如何。
上下为道字。恐只是一意。所论得之。
木俱有为柯之理。而在手之柯先见用。故先为柯。人皆有为人之道。而治人之人先能觉。故先尽道。以未为柯之木。摹已为柯之木而用在此为柯之理。正犹以未觉道之人。效已觉道之人而行在我为人之道也。有以彼此柯为远者则亦岂无以彼此人为远者哉。面目甚同。恐未有差殊意。
极言之则固如此。然伐柯者其大小长短。必取则于所执之柯。治人者但责以其人之所能知能行而已。何尝教他视我所知以为知。视我所行以为行乎。此当就事上论。不必就理上深看。
章下谓道不远人者。夫妇所能。丘未能一者。圣人所不能。圣人之道或远人以为者乎。夫子之言谦辞而已。岂真有不能也。朱子曰事父必如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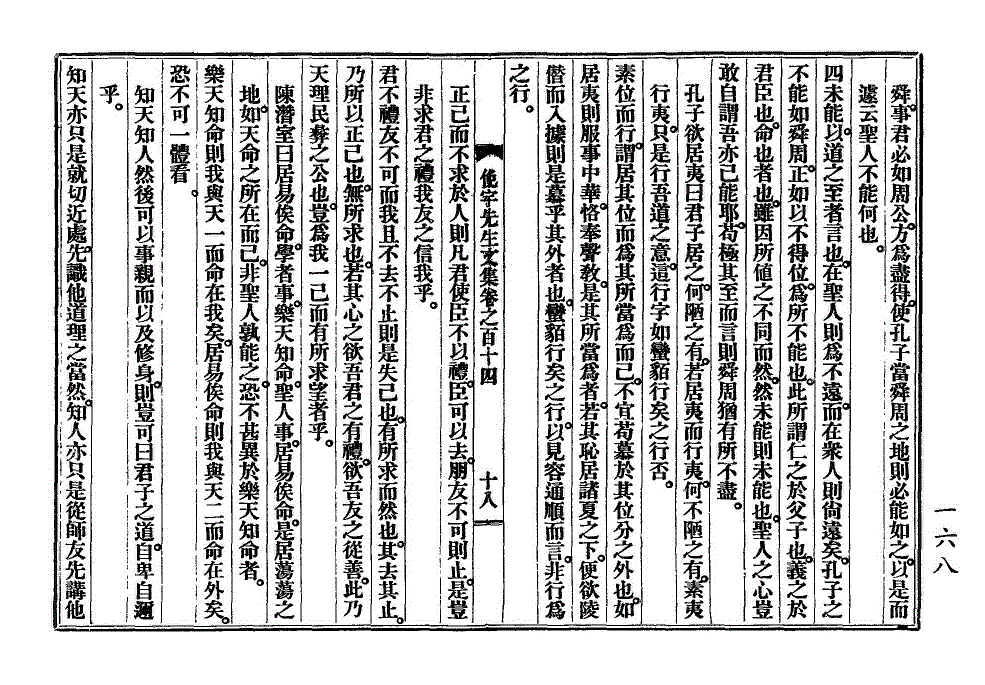 舜。事君必如周公。方为尽得。使孔子当舜周之地则必能如之。以是而遽云圣人不能何也。
舜。事君必如周公。方为尽得。使孔子当舜周之地则必能如之。以是而遽云圣人不能何也。四未能。以道之至者言也。在圣人则为不远。而在众人则尚远矣。孔子之不能如舜周。正如以不得位。为所不能也。此所谓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者也。虽因所值之不同而然。然未能则未能也。圣人之心岂敢自谓吾亦已能耶。苟极其至而言则舜周犹有所不尽。
孔子欲居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若居夷而行夷。何不陋之有。素夷行夷。只是行吾道之意。这行字如蛮貊行矣之行否。
素位而行。谓居其位而为其所当为而已。不宜苟慕于其位分之外也。如居夷则服事中华。恪奉声教。是其所当为者。若其耻居诸夏之下。便欲陵僭而入据则是慕乎其外者也。蛮貊行矣之行。以见容通顺而言。非行为之行。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凡君使臣不以礼。臣可以去。朋友不可则止。是岂非求君之礼我友之信我乎。
君不礼友不可而我且不去不止则是失己也。有所求而然也。其去其止。乃所以正己也。无所求也。若其心之欲吾君之有礼。欲吾友之从善。此乃天理民彝之公也。岂为我一己而有所求望者乎。
陈潜室曰居易俟命。学者事。乐天知命。圣人事。居易俟命。是居荡荡之地。如天命之所在而已。非圣人孰能之。恐不甚异于乐天知命者。
乐天知命则我与天一而命在我矣。居易俟命则我与天二而命在外矣。恐不可一体看。
知天知人然后可以事亲而以及修身。则岂可曰君子之道。自卑自迩乎。
知天亦只是就切近处。先识他道理之当然。知人亦只是从师友先讲他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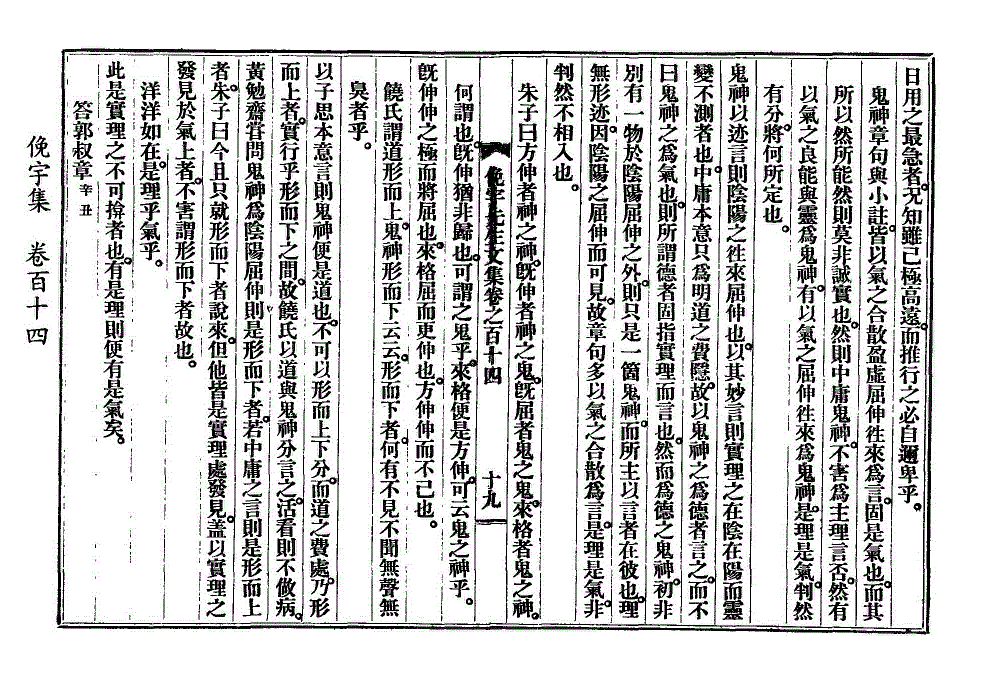 日用之最急者。况知虽已极高远。而推行之必自迩卑乎。
日用之最急者。况知虽已极高远。而推行之必自迩卑乎。鬼神章句与小注。皆以气之合散盈虚屈伸往来为言。固是气也。而其所以然所能然则莫非诚实也。然则中庸鬼神。不害为主理言否。然有以气之良能与灵为鬼神。有以气之屈伸往来为鬼神。是理是气。判然有分。将何所定也。
鬼神以迹言则阴阳之往来屈伸也。以其妙言则实理之在阴在阳而灵变不测者也。中庸本意只为明道之费隐。故以鬼神之为德者言之。而不曰鬼神之为气也。则所谓德者固指实理而言也。然而为德之鬼神。初非别有一物于阴阳屈伸之外。则只是一个鬼神。而所主以言者在彼也。理无形迹。因阴阳之屈伸而可见。故章句多以气之合散为言。是理是气。非判然不相入也。
朱子曰方伸者神之神。既伸者神之鬼。既屈者鬼之鬼。来格者鬼之神。何谓也。既伸犹非归也。可谓之鬼乎。来格便是方伸。可云鬼之神乎。
既伸伸之极而将屈也。来格屈而更伸也。方伸伸而不已也。
饶氏谓道形而上。鬼神形而下云云。形而下者。何有不见不闻无声无臭者乎。
以子思本意言则鬼神便是道也。不可以形而上下分。而道之费处。乃形而上者。实行乎形而下之间。故饶氏以道与鬼神分言之。活看则不做病。黄勉斋尝问鬼神为阴阳屈伸则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则是形而上者。朱子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说来。但他皆是实理处发见。盖以实理之发见于气上者。不害谓形而下者故也。
洋洋如在。是理乎气乎。
此是实理之不可掩者也。有是理则便有是气矣。
答郭叔章(辛丑)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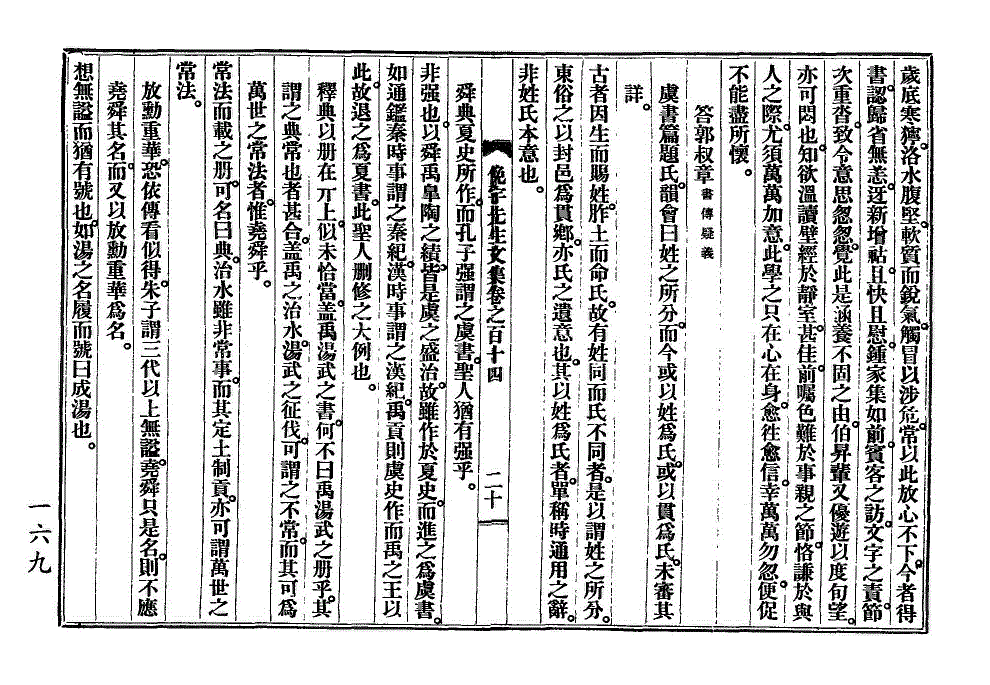 岁底寒狞。洛水腹坚。软质而锐气。触冒以涉危。常以此放心不下。今者得书。认归省无恙。迓新增祜。且快且慰。钟家集如前。宾客之访。文字之责。节次重沓。致令意思匆匆。觉此是涵养不固之由。伯升辈又优游以度旬望。亦可闷也。知欲温读壁经于静室。甚佳。前嘱色难于事亲之节。恪谦于与人之际。尤须万万加意。此学之只在心在身。愈往愈信。幸万万勿忽。便促不能尽所怀。
岁底寒狞。洛水腹坚。软质而锐气。触冒以涉危。常以此放心不下。今者得书。认归省无恙。迓新增祜。且快且慰。钟家集如前。宾客之访。文字之责。节次重沓。致令意思匆匆。觉此是涵养不固之由。伯升辈又优游以度旬望。亦可闷也。知欲温读壁经于静室。甚佳。前嘱色难于事亲之节。恪谦于与人之际。尤须万万加意。此学之只在心在身。愈往愈信。幸万万勿忽。便促不能尽所怀。答郭叔章(书传疑义)
虞书篇题氏。韵会曰姓之所分。而今或以姓为氏。或以贯为氏。未审其详。
古者因生而赐姓。胙土而命氏。故有姓同而氏不同者。是以谓姓之所分。东俗之以封邑为贯乡。亦氏之遗意也。其或(저본에는 빠져 있는데, 정오표에 따라 ‘或’ 자를 보충하였다.)以姓为氏者。单称时通用之辞。非姓氏本意也。
舜典夏史所作。而孔子强谓之虞书。圣人犹有强乎。
非强也。以舜禹皋陶之绩。皆是虞之盛治。故虽作于夏史。而进之为虞书。如通鉴秦时事谓之秦纪。汉时事谓之汉纪。禹贡则虞史作而禹之王以此。故退之为夏书。此圣人删修之大例也。
释典以册在丌上。似未恰当。盖禹汤武之书。何不曰禹汤武之册乎。其谓之典常也者甚合。盖禹之治水。汤武之征伐。可谓之不常。而其可为万世之常法者。惟尧舜乎。
常法而载之册。可名曰典。治水虽非常事。而其定土制贡。亦可谓万世之常法。
放勋重华。恐依传看似得。朱子谓三代以上无谥。尧舜只是名。则不应尧舜其名。而又以放勋重华为名。
想无谥而犹有号也。如汤之名履而号曰成汤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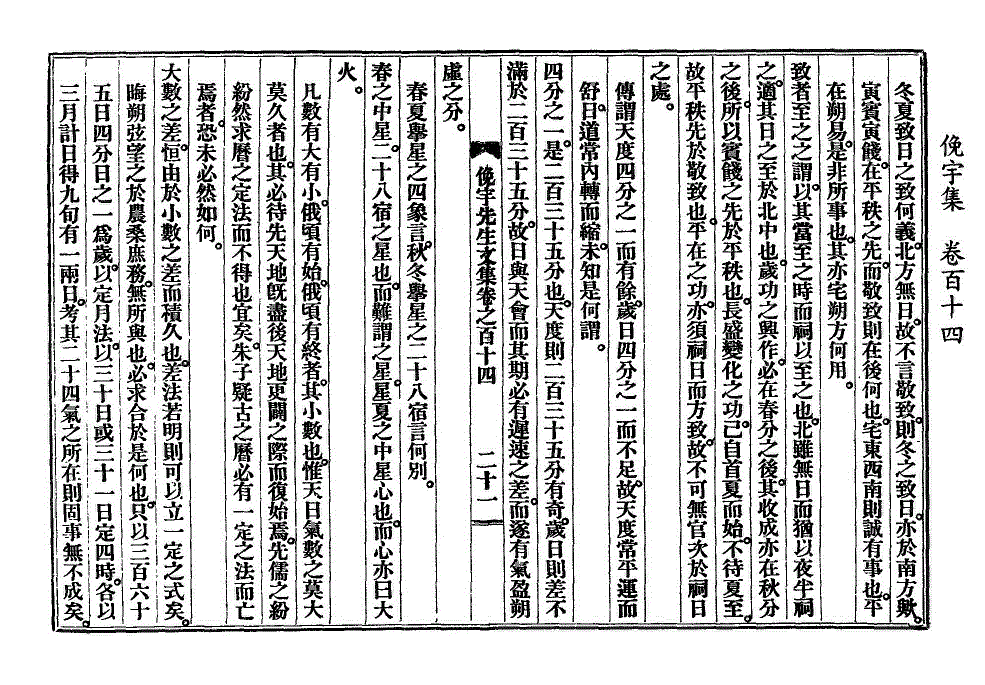 冬夏致日之致何义。北方无日。故不言敬致。则冬之致日。亦于南方欤。寅宾寅饯。在平秩之先。而敬致则在后何也。宅东西南则诚有事也。平在朔易。是非所事也。其亦宅朔方何用。
冬夏致日之致何义。北方无日。故不言敬致。则冬之致日。亦于南方欤。寅宾寅饯。在平秩之先。而敬致则在后何也。宅东西南则诚有事也。平在朔易。是非所事也。其亦宅朔方何用。致者至之之谓。以其当至之时而祠以至之也。北虽无日而犹以夜半祠之。适其日之至于北中也。岁功之兴作。必在春分之后。其收成亦在秋分之后。所以宾饯之先于平秩也。长盛变化之功。已自首夏而始。不待夏至。故平秩先于敬致也。平在之功。亦须祠日而方致。故不可无官次于祠日之处。
传谓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馀。岁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运而舒。日道常内转而缩。未知是何谓。
四分之一。是二百三十五分也。天度则二百三十五分有奇。岁日则差不满于二百三十五分。故日与天会而其期必有迟速之差。而遂有气盈朔虚之分。
春夏举星之四象言。秋冬举星之二十八宿言何别。
春之中星。二十八宿之星也。而难谓之星。星夏之中星心也。而心亦曰大火。
凡数有大有小。俄顷有始。俄顷有终者。其小数也。惟天日气数之莫大莫久者也。其必待先天地既尽后天地更辟之际而复始焉。先儒之纷纷然求历之定法而不得也宜矣。朱子疑古之历必有一定之法而亡焉者。恐未必然如何。
大数之差。恒由于小数之差而积久也。差法若明则可以立一定之式矣。
晦朔弦望之于农桑庶务。无所与也。必求合于是何也。只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为岁。以定月法。以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定四时。各以三月计日得九旬有一两日。考其二十四气之所在则固事无不成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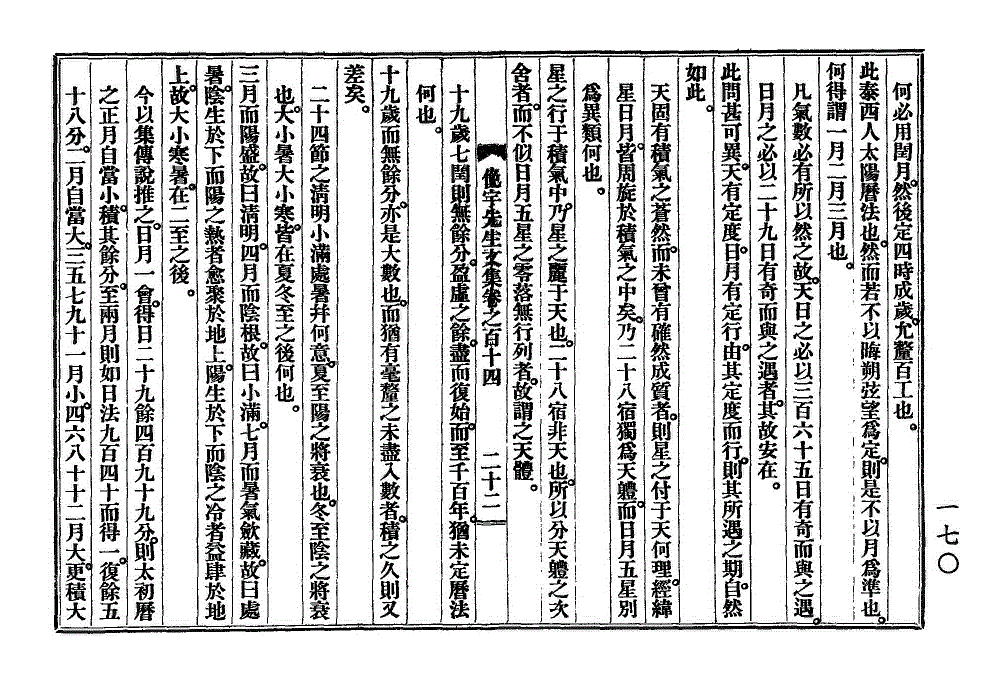 何必用闰月。然后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也。
何必用闰月。然后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也。此泰西人太阳历法也。然而若不以晦朔弦望为定。则是不以月为准也。何得谓一月二月三月也。
凡气数必有所以然之故。天日之必以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与之遇。日月之必以二十九日有奇而与之遇者。其故安在。
此问甚可异。天有定度。日月有定行。由其定度而行。则其所遇之期。自然如此。
天固有积气之苍然。而未曾有确然成质者。则星之付于天何理。经纬星日月。皆周旋于积气之中矣。乃二十八宿独为天体。而日月五星别为异类何也。
星之行于积气中。乃星之丽于天也。二十八宿非天也。所以分天体之次舍者。而不似日月五星之零落无行列者。故谓之天体。
十九岁七闰则无馀分。盈虚之馀。尽而复始。而至千百年。犹未定历法何也。
十九岁而无馀分。亦是大数也。而犹有毫釐之未尽入数者。积之久则又差矣。
二十四节之清明小满处暑并何意。夏至阳之将衰也。冬至阴之将衰也。大小暑大小寒。皆在夏冬至之后何也。
三月而阳盛。故曰清明。四月而阴根。故曰小满。七月而暑气敛藏。故曰处暑。阴生于下而阳之热者愈聚于地上。阳生于下而阴之冷者益肆于地上。故大小寒暑。在二至之后。
今以集传说推之。日月一会。得日二十九馀四百九十九分。则太初历之正月自当小。积其馀分。至两月则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一。复馀五十八分。二月自当大。三五七九十一月小。四六八十十二月大。更积大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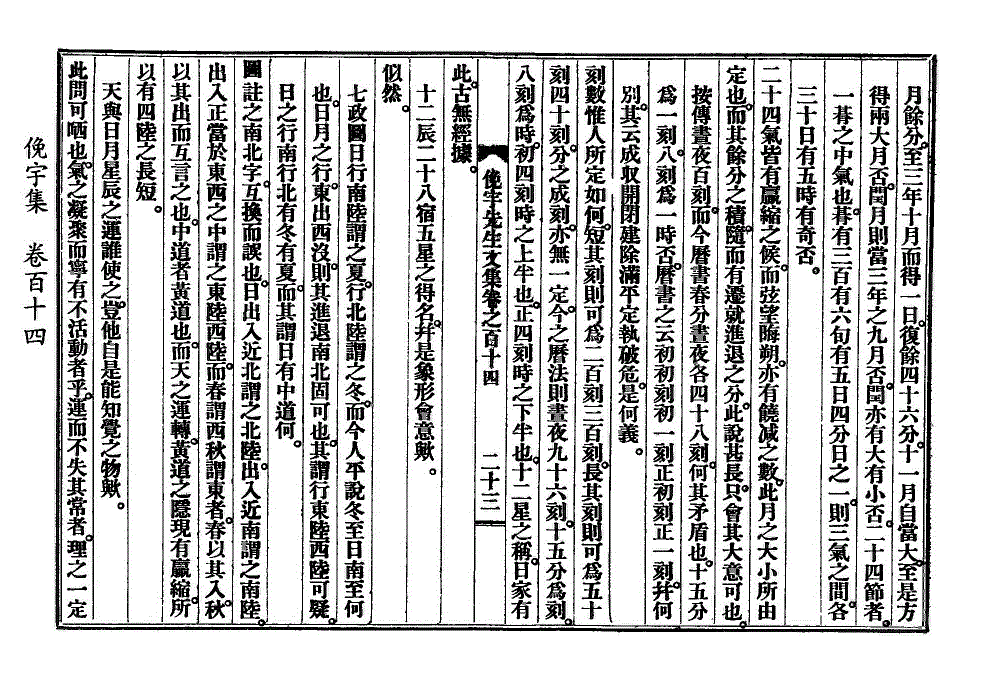 月馀分。至三年十月而得一日。复馀四十六分。十一月自当大。至是方得两大月否。闰月则当三年之九月否。闰亦有大有小否。二十四节者。一期之中气也。期有三百有六旬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则三气之间。各三十日有五时有奇否。
月馀分。至三年十月而得一日。复馀四十六分。十一月自当大。至是方得两大月否。闰月则当三年之九月否。闰亦有大有小否。二十四节者。一期之中气也。期有三百有六旬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则三气之间。各三十日有五时有奇否。二十四气皆有赢缩之候。而弦望晦朔。亦有饶减之数。此月之大小所由定也。而其馀分之积。随而有迁就进退之分。此说甚长。只会其大意可也。
按传昼夜百刻。而今历书春分昼夜各四十八刻。何其矛盾也。十五分为一刻。八刻为一时否。历书之云初初刻初一刻正初刻正一刻。并何别。其云成收开闭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是何义。
刻数惟人所定如何。短其刻则可为二百刻三百刻。长其刻则可为五十刻四十刻。分之成刻。亦无一定。今之历法则昼夜九十六刻。十五分为刻。八刻为时。初四刻时之上半也。正四刻时之下半也。十二星之称。日家有此。古无经据。
十二辰二十八宿五星之得名。并是象形会意欤。
似然。
七政图日行南陆谓之夏。行北陆谓之冬。而今人平说冬至日南至何也。日月之行。东出西没。则其进退南北固可也。其谓行东陆西陆可疑。日之行南行北有冬有夏。而其谓日有中道何。
图注之南北字。互换而误也。日出入近北谓之北陆。出入近南谓之南陆。出入正当于东西之中谓之东陆西陆。而春谓西秋谓东者。春以其入。秋以其出而互言之也。中道者黄道也。而天之运转。黄道之隐现有赢缩。所以有四陆之长短。
天与日月星辰之运谁使之。岂他自是能知觉之物欤。
此问可哂也。气之凝聚而宁有不活动者乎。运而不失其常者。理之一定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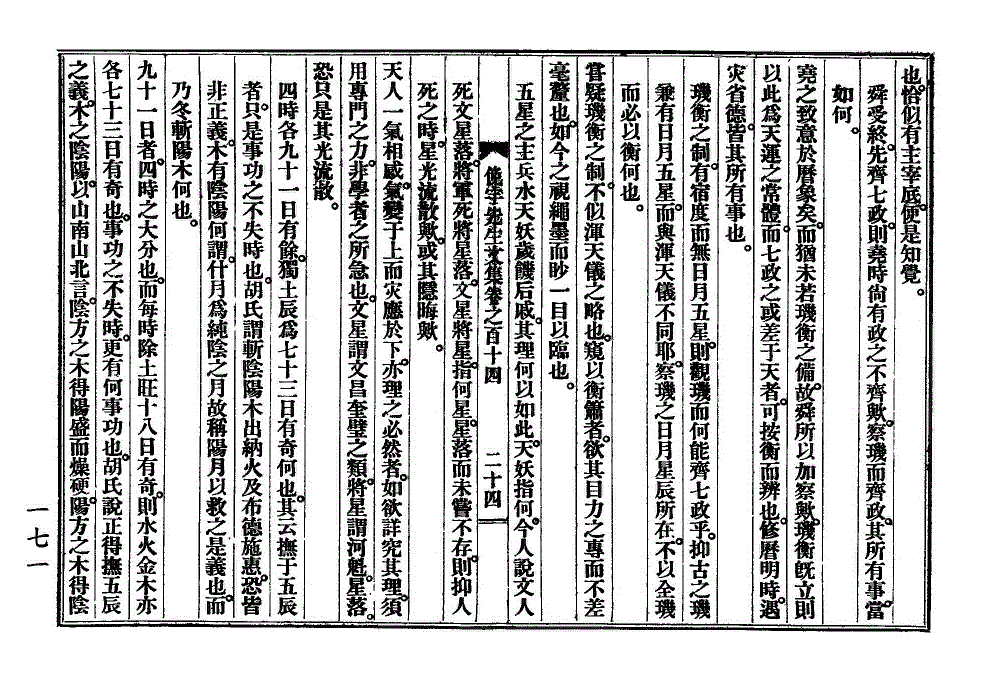 也。恰似有主宰底。便是知觉。
也。恰似有主宰底。便是知觉。舜受终。先齐七政。则尧时尚有政之不齐欤。察玑而齐政。其所有事。当如何。
尧之致意于历象矣。而犹未若玑衡之备。故舜所以加察欤。玑衡既立则以此为天运之常体。而七政之或差于天者。可按衡而辨也。修历明时。遇灾省德。皆其所有事也。
玑衡之制。有宿度而无日月五星。则观玑而何能齐七政乎。抑古之玑兼有日月五星。而与浑天仪不同耶。察玑之日月星辰所在。不以全玑而必以衡何也。
尝疑玑衡之制。不似浑天仪之略也。窥以衡箫者。欲其目力之专而不差毫釐也。如今之视绳墨而眇一目以临也。
五星之主兵水天妖岁饥后戚。其理何以如此。天妖指何。今人说文人死文星落。将军死将星落。文星将星。指何星。星落而未尝不存。则抑人死之时。星光流散欤。或其隐晦欤。
天人一气相感。气变于上而灾应于下。亦理之必然者。如欲详究其理。须用专门之力。非学者之所急也。文星谓文昌奎璧之类。将星谓河魁。星落。恐只是其光流散。
四时各九十一日有馀。独土辰为七十三日有奇何也。其云抚于五辰者。只是事功之不失时也。胡氏谓斩阴阳木出纳火及布德施惠。恐皆非正义。木有阴阳何谓。什月为纯阴之月故称阳月以救之是义也。而乃冬斩阳木何也。
九十一日者。四时之大分也。而每时除土旺十八日有奇。则水火金木亦各七十三日有奇也。事功之不失时。更有何事功也。胡氏说正得抚五辰之义。木之阴阳。以山南山北言。阴方之木得阳盛而燥硬。阳方之木得阴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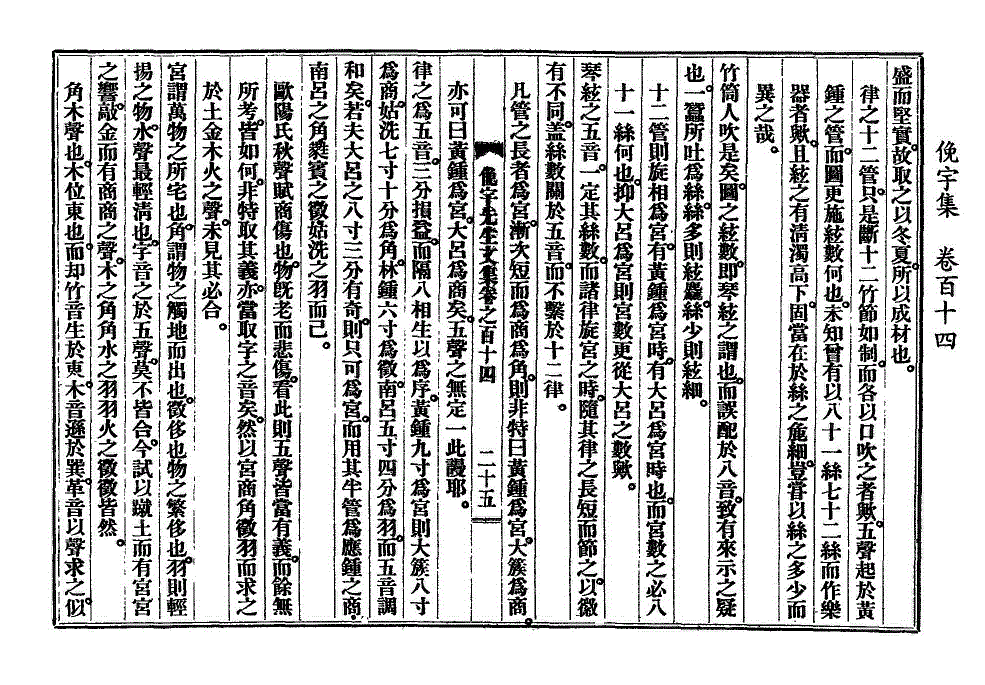 盛而坚实。故取之以冬夏。所以成材也。
盛而坚实。故取之以冬夏。所以成材也。律之十二管。只是断十二竹节如制。而各以口吹之者欤。五声起于黄钟之管。而图更施弦数何也。未知曾有以八十一丝七十二丝而作乐器者欤。且弦之有清浊高下。固当在于丝之粗细。岂尝以丝之多少而异之哉。
竹筒人吹是矣。图之弦数。即琴弦之谓也。而误配于八音。致有来示之疑也。一蚕所吐为丝。丝多则弦粗。丝少则弦细。
十二管则旋相为宫。有黄钟为宫时。有大吕为宫时也。而宫数之必八十一丝何也。抑大吕为宫则宫数更从大吕之数欤。
琴弦之五音。一定其丝数。而诸律旋宫之时。随其律之长短而节之。以徽有不同。盖丝数关于五音。而不系于十二律。
凡管之长者为宫。渐次短而为商为角。则非特曰黄钟为宫。大簇为商。亦可曰黄钟为宫。大吕为商矣。五声之无定一此谩耶。
律之为五音。三分损益。而隔八相生以为序。黄钟九寸为宫则大簇八寸为商。姑洗七寸十分为角。林钟六寸为徵。南吕五寸四分为羽。而五音调和矣。若夫大吕之八寸三分有奇。则只可为宫。而用其半管为应钟之商,南吕之角,蕤宾之徵,姑洗之羽而已。
欧阳氏秋声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看此则五声皆当有义。而馀无所考。皆如何。非特取其义。亦当取字之音矣。然以宫商角徵羽而求之于土金木火之声。未见其必合。
宫谓万物之所宅也。角谓物之触地而出也。徵侈也物之繁侈也。羽则轻扬之物。水声最轻清也。字音之于五声。莫不皆合。今试以蹴土而有宫宫之响。敲金而有商商之声。本之角角水之羽羽火之徵徵皆然。
角木声也。木位东也。而却竹音生于东。木音逊于巽。革音以声求之。似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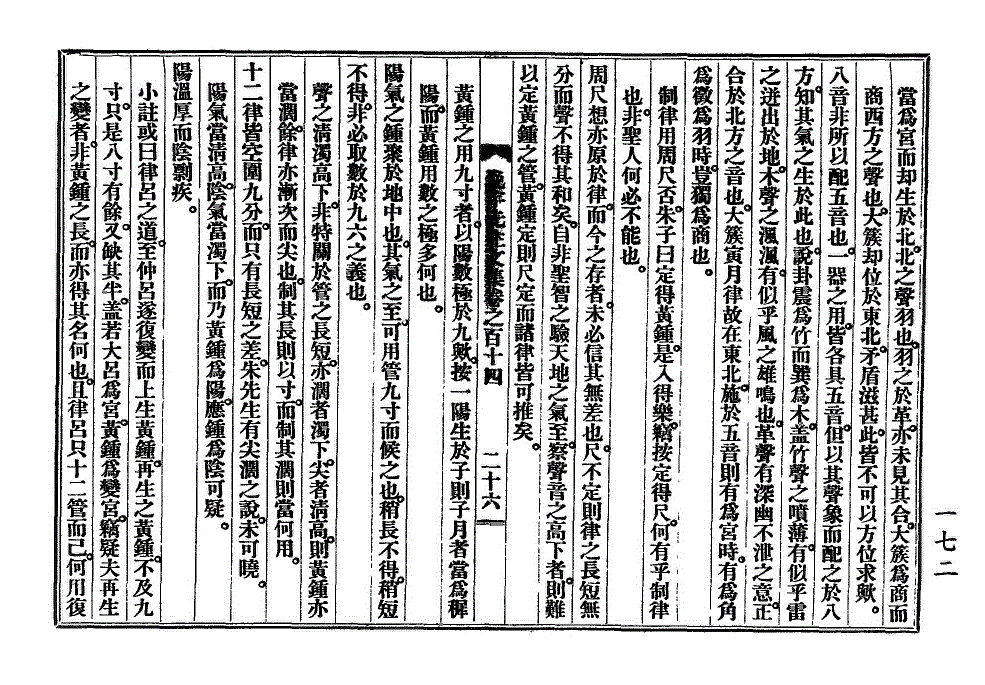 当为宫而却生于北。北之声羽也。羽之于革。亦未见其合。大簇为商而商西方之声也。大簇却位于东北。矛盾滋甚。此皆不可以方位求欤。
当为宫而却生于北。北之声羽也。羽之于革。亦未见其合。大簇为商而商西方之声也。大簇却位于东北。矛盾滋甚。此皆不可以方位求欤。八音非所以配五音也。一器之用。皆各具五音。但以其声象而配之于八方。知其气之生于此也。说卦震为竹而巽为木。盖竹声之喷薄。有似乎雷之迸出于地。木声之沨沨。有似乎风之雄鸣也。革声有深幽不泄之意。正合于北方之音也。大簇寅月律故在东北。施于五音则有为宫时。有为角为徵为羽时。岂独为商也。
制律用周尺否。朱子曰定得黄钟。是入得乐。窃按定得尺。何有乎制律也。非圣人何必不能也。
周尺想亦原于律。而今之存者。未必信其无差也。尺不定则律之长短无分而声不得其和矣。自非圣智之验天地之气至。察声音之高下者。则难以定黄钟之管。黄钟定则尺定而诸律皆可推矣。
黄钟之用九寸者。以阳数极于九欤。按一阳生于子则子月者当为稚阳。而黄钟用数之极多何也。
阳气之钟聚于地中也。其气之至。可用管九寸而候之也。稍长不得。稍短不得。非必取数于九六之义也。
声之清浊高下。非特关于管之长短。亦阔者浊下。尖者清高。则黄钟亦当阔。馀律亦渐次而尖也。制其长则以寸。而制其阔则当何用。
十二律皆空围九分。而只有长短之差。朱先生有尖阔之说。未可晓。
阳气当清高。阴气当浊下。而乃黄钟为阳。应钟为阴可疑。
阳温厚而阴剽疾。
小注或曰律吕之道。至仲吕遂复变而上生黄钟。再生之黄钟。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馀。又缺其半。盖若大吕为宫。黄钟为变宫。窃疑夫再生之变者。非黄钟之长。而亦得其名何也。且律吕只十二管而已。何用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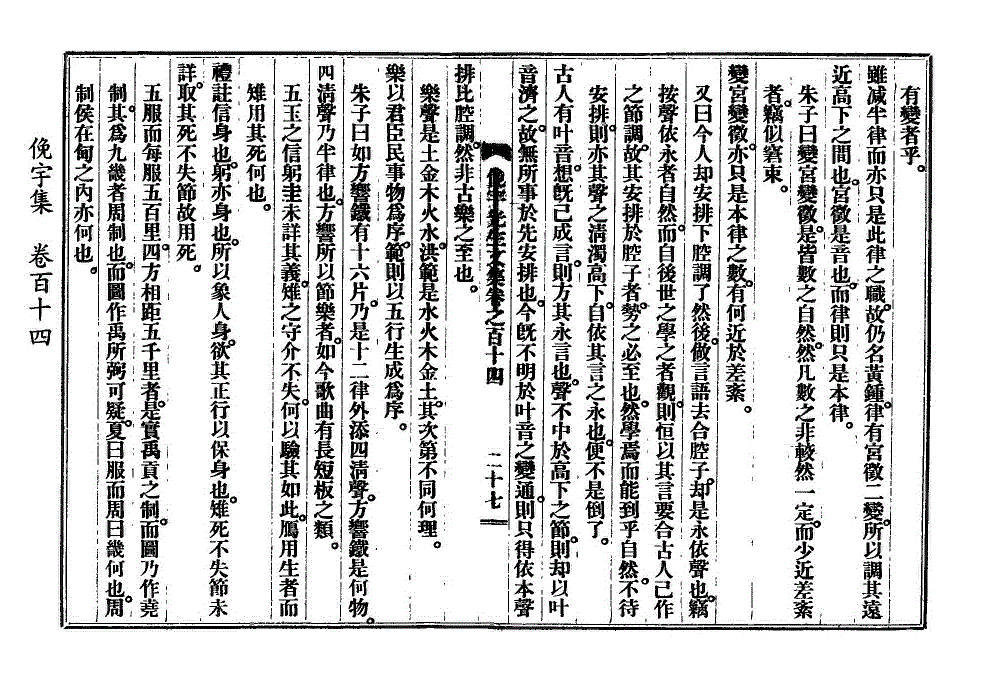 有变者乎。
有变者乎。虽减半律而亦只是此律之职。故仍名黄钟。律有宫徵二变。所以调其远近高下之间也。宫徵是音也。而律则只是本律。
朱子曰变宫变徵。是皆数之自然。然凡数之非较然一定。而少近差紊者。窃似窘束。
变宫变徵。亦只是本律之数。有何近于差紊。
又曰今人却安排下腔调了然后。做言语去合腔子。却是永依声也。窃按声依永者自然。而自后世之学之者观。则恒以其言要合古人已作之节调。故其安排于腔子者。势之必至也。然学焉而能到乎自然。不待安排。则亦其声之清浊高下。自依其言之永也。便不是倒了。
古人有叶音。想既已成言。则方其永言也。声不中于高下之节。则却以叶音济之。故无所事于先安排也。今既不明于叶音之变通。则只得依本声排比腔调。然非古乐之至也。
乐声是土金木火水。洪范是水火木金土。其次第不同何理。
乐以君臣民事物为序。范则以五行生成为序。
朱子曰如方响铁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声。方响铁是何物。
四清声乃半律也。方响所以节乐者。如今歌曲有长短板之类。
五玉之信躬圭未详其义。雉之守介不失。何以验其如此。雁用生者而雉用其死何也。
礼注信身也。躬亦身也。所以象人身。欲其正行以保身也。雉死不失节未详。取其死不失节故用死。
五服而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五千里者。是实禹贡之制。而图乃作尧制。其为九畿者周制也。而图作禹所弼可疑。夏曰服而周曰畿何也。周制侯在甸之内亦何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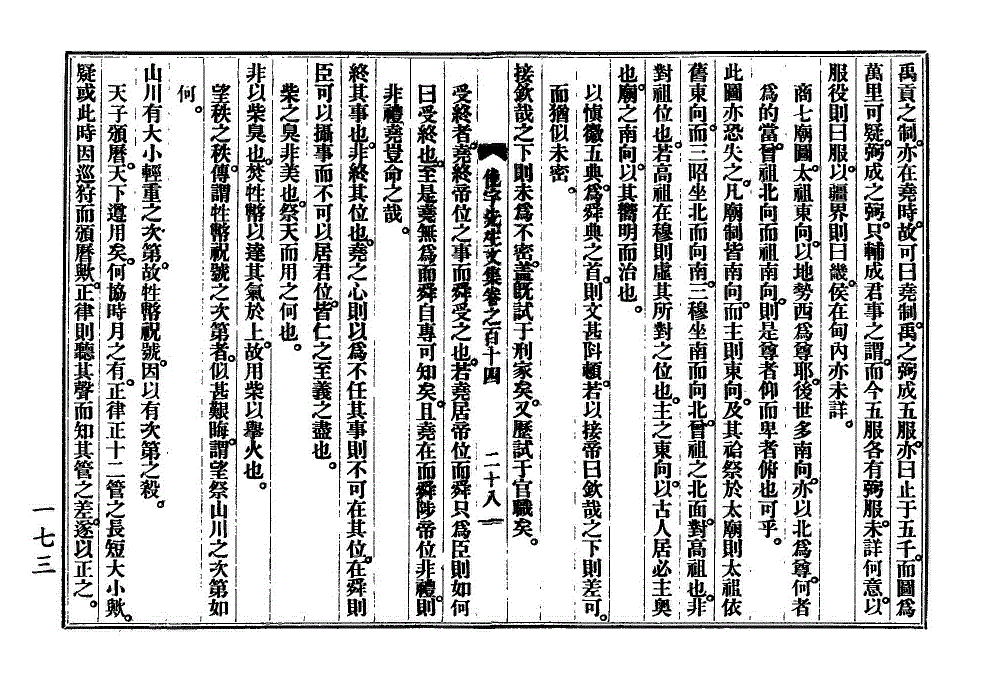 禹贡之制。亦在尧时。故可曰尧制。禹之弼成五服。亦曰止于五千。而图为万里可疑。弼成之弼。只辅成君事之谓。而今五服各有弼服。未详何意。以服役则曰服。以疆界则曰畿。侯在甸内亦未详。
禹贡之制。亦在尧时。故可曰尧制。禹之弼成五服。亦曰止于五千。而图为万里可疑。弼成之弼。只辅成君事之谓。而今五服各有弼服。未详何意。以服役则曰服。以疆界则曰畿。侯在甸内亦未详。商七庙图。太祖东向。以地势西为尊耶。后世多南向。亦以北为尊。何者为的当。曾祖北向而祖南向。则是尊者仰而卑者俯也可乎。
此图亦恐失之。凡庙制皆南向。而主则东向。及其祫祭于太庙则太祖依旧东向。而三昭坐北而向南。三穆坐南而向北。曾祖之北面。对高祖也。非对祖位也。若高祖在穆则虚其所对之位也。主之东向。以古人居必主奥也。庙之南向。以其向明而治也。
以慎徽五典。为舜典之首。则文甚陡顿。若以接帝曰钦哉之下则差可。而犹似未密。
接钦哉之下则未为不密。盖既试于刑家矣。又历试于官职矣。
受终者。尧终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若尧居帝位而舜只为臣则如何曰受终也。至是尧无为而舜自专可知矣。且尧在而舜陟帝位非礼。则非礼尧岂命之哉。
终其事也。非终其位也。尧之心则以为不任其事则不可在其位。在舜则臣可以摄事而不可以居君位。皆仁之至义之尽也。
柴之臭非美也。祭天而用之何也。
非以柴臭也。焚牲币以达其气于上。故用柴以举火也。
望秩之秩。传谓牲币祝号之次第者。似甚艰晦。谓望祭山川之次第如何。
山川有大小轻重之次第。故牲币祝号。因以有次第之杀。
天子颁历。天下遵用矣。何协时月之有。正律正十二管之长短大小欤。
疑或此时因巡狩而颁历欤。正律则听其声而知其管之差。遂以正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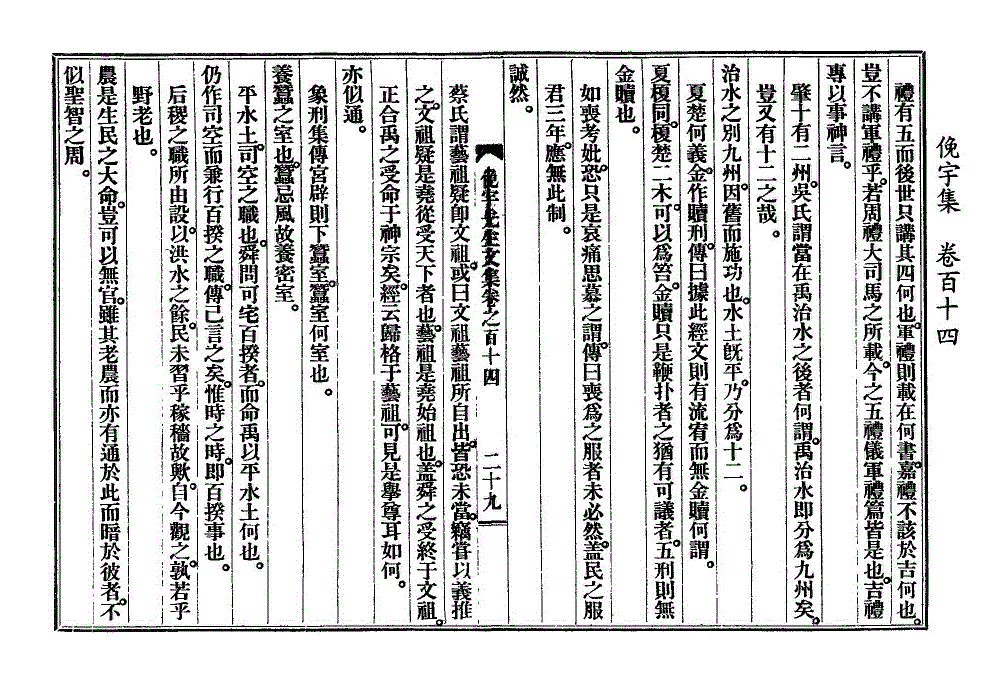 礼有五而后世只讲其四何也。军礼则载在何书。嘉礼不该于吉何也。
礼有五而后世只讲其四何也。军礼则载在何书。嘉礼不该于吉何也。岂不讲军礼乎。若周礼大司马之所载。今之五礼仪军礼篇皆是也。吉礼专以事神言。
肇十有二州。吴氏谓当在禹治水之后者何谓。禹治水即分为九州矣。岂又有十二之哉。
治水之别九州。因旧而施功也。水土既平。乃分为十二。
夏楚何义。金作赎刑。传曰据此经文则有流宥而无金赎何谓。
夏槚同。槚楚二木。可以为笞。金赎只是鞭扑者之犹有可议者。五刑则无金赎也。
如丧考妣。恐只是哀痛思慕之谓。传曰丧为之服者未必然。盖民之服君三年。应无此制。
诚然。
蔡氏谓艺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艺祖所自出。皆恐未当。窃尝以义推之。文祖疑是尧从受天下者也。艺祖是尧始祖也。盖舜之受终于文祖。正合禹之受命于神宗矣。经云归格于艺祖。可见是举尊耳如何。
亦似通。
象刑集传宫辟则下蚕室。蚕室何室也。
养蚕之室也。蚕忌风故养密室。
平水土。司空之职也。舜问可宅百揆者。而命禹以平水土何也。
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职。传已言之矣。惟时之时。即百揆事也。
后稷之职所由设。以洪水之馀。民未习乎稼穑故欤。自今观之。孰若乎野老也。
农是生民之大命。岂可以无官。虽其老农而亦有通于此而暗于彼者。不似圣智之周。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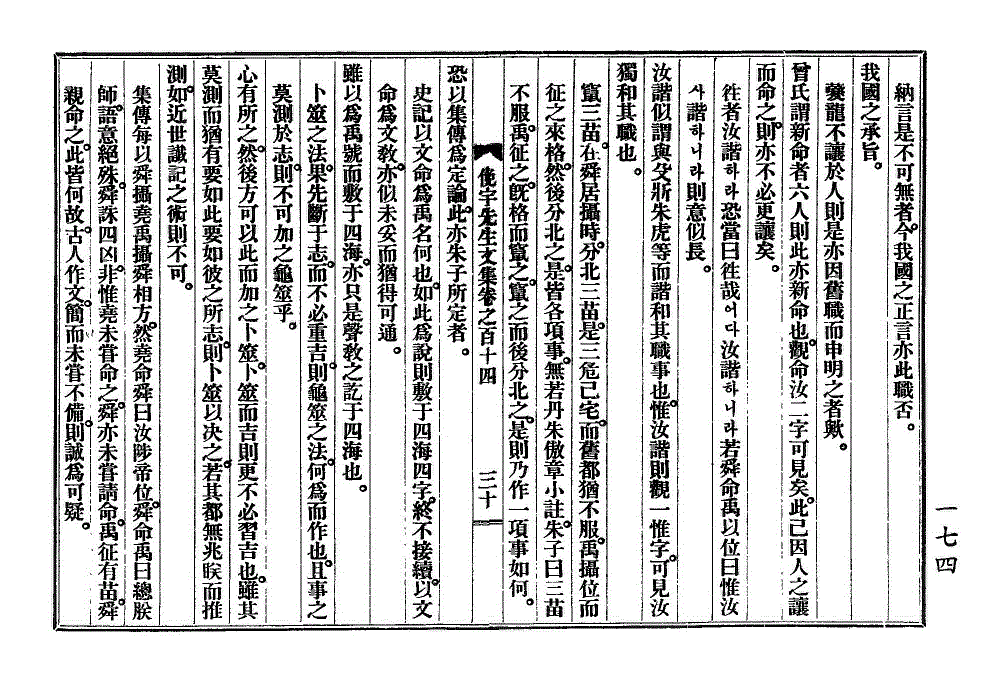 纳言是不可无者。今我国之正言亦此职否。
纳言是不可无者。今我国之正言亦此职否。我国之承旨。
夔龙不让于人则是亦因旧职而申明之者欤。
曾氏谓新命者六人则此亦新命也。观命汝二字可见矣。此已因人之让而命之。则亦不必更让矣。
往哉汝谐하라恐当曰往哉어다汝谐하니라若舜命禹以位曰惟汝사谐하니라则意似长。
汝谐似谓与殳斨朱虎等而谐和其职事也。惟汝谐则观一惟字。可见汝独和其职也。
窜三苗。在舜居摄时。分北三苗。是三危已宅。而旧都犹不服。禹摄位而征之来格。然后分北之。是皆各项事。无若丹朱傲章小注。朱子曰三苗不服。禹征之。既格而窜之。窜之而后分北之。是则乃作一项事如何。
恐以集传为定论。此亦朱子所定者。
史记以文命为禹名何也。如此为说则敷于四海四字。终不接续。以文命为文教。亦似未妥而犹得可通。
虽以为禹号而敷于四海。亦只是声教之讫于四海也。
卜筮之法。果先断于志。而不必重吉。则龟筮之法。何为而作也。且事之莫测于志。则不可加之龟筮乎。
心有所之。然后方可以此而加之卜筮。卜筮而吉则更不必习吉也。虽其莫测而犹有要如此要如彼之所志。则卜筮以决之。若其都无兆眹而推测。如近世谶记之术则不可。
集传每以舜摄尧禹摄舜相方。然尧命舜曰汝陟帝位。舜命禹曰总朕师。语意绝殊。舜诛四凶。非惟尧未尝命之。舜亦未尝请命。禹征有苗。舜亲命之。此皆何故。古人作文。简而未尝不备。则诚为可疑。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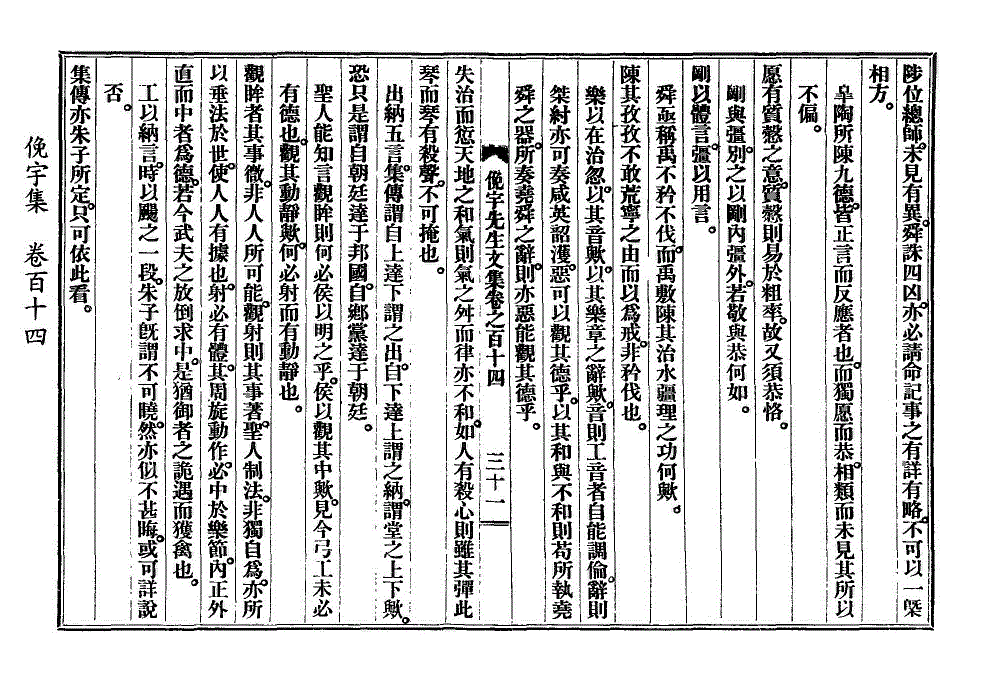 陟位总师。未见有异。舜诛四凶。亦必请命记事之有详有略。不可以一槩相方。
陟位总师。未见有异。舜诛四凶。亦必请命记事之有详有略。不可以一槩相方。皋陶所陈九德。皆正言而反应者也。而独愿而恭。相类而未见其所以不偏。
愿有质悫之意。质悫则易于粗率。故又须恭恪。
刚与彊。别之以刚内彊外。若敬与恭何如。
刚以体言。彊以用言。
舜亟称禹不矜不伐。而禹敷陈其治水疆理之功何欤。
陈其孜孜不敢荒宁之由而以为戒。非矜伐也。
乐以在治忽。以其音欤。以其乐章之辞欤。音则工音者自能调伦。辞则桀纣亦可奏咸英韶濩。恶可以观其德乎。以其和与不和则苟所执尧舜之器。所奏尧舜之辞。则亦恶能观其德乎。
失治而愆天地之和气则气之舛而律亦不和。如人有杀心则虽其弹此琴而琴有杀声。不可掩也。
出纳五言。集传谓自上达下谓之出。自下达上谓之纳。谓堂之上下欤。
恐只是谓自朝廷达于邦国。自乡党达于朝廷。
圣人能知言观眸则何必侯以明之乎。侯以观其中欤。见今弓工未必有德也。观其动静欤。何必射而有动也。
观眸者其事微。非人人所可能。观射则其事著。圣人制法。非独自为。亦所以垂法于世。使人人有据也。射必有体。其周旋动作。必中于乐节。内正外直而中者为德。若今武夫之放倒求中。是犹御者之诡遇而获禽也。
工以纳言。时以飏之一段。朱子既谓不可晓。然亦似不甚晦。或可详说否。
集传亦朱子所定。只可依此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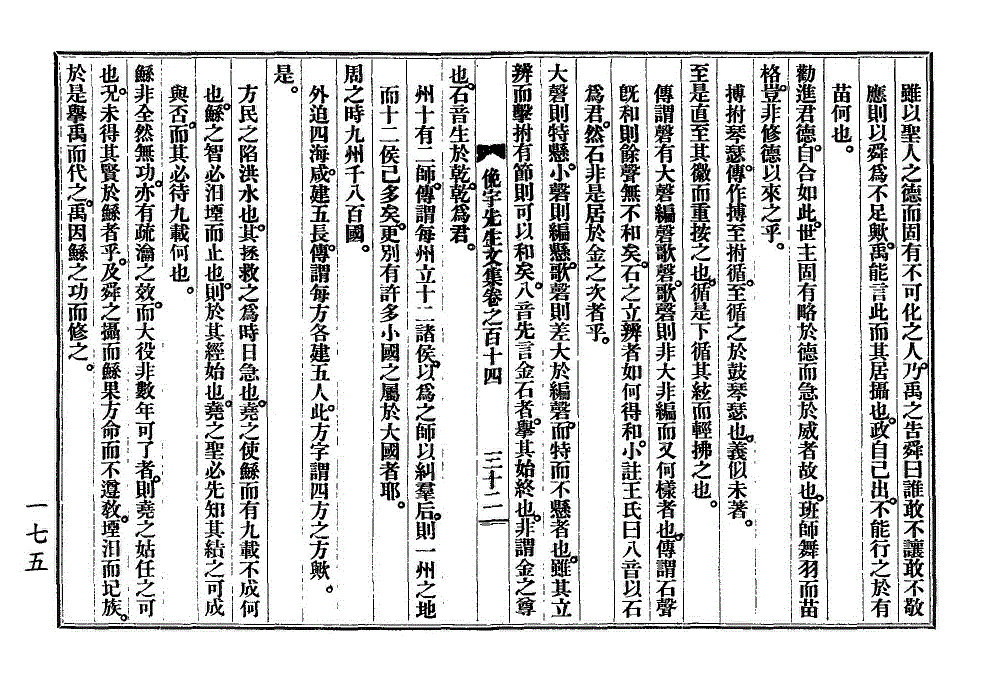 虽以圣人之德而固有不可化之人。乃禹之告舜曰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则以舜为不足欤。禹能言此而其居摄也。政自己出。不能行之于有苗何也。
虽以圣人之德而固有不可化之人。乃禹之告舜曰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则以舜为不足欤。禹能言此而其居摄也。政自己出。不能行之于有苗何也。劝进君德。自合如此。世主固有略于德而急于威者故也。班师舞羽而苗格。岂非修德以来之乎。
搏拊琴瑟。传作搏至拊循。至循之于鼓琴瑟也。义似未著。
至是直至其徽而重按之也。循是下循其弦而轻拂之也。
传谓磬有大磬编磬歌磬。歌磬则非大非编而又何样者也。传谓石声既和则馀声无不和矣。石之立辨者如何得和。小注王氏曰八音以石为君。然石非是居于金之次者乎。
大磬则特悬。小磬则编悬。歌磬则差大于编磬。而特而不悬者也。虽其立辨而击拊有节则可以和矣。八音先言金石者。举其始终也。非谓金之尊也。石音生于乾。乾为君。
州十有二师。传谓每州立十二诸侯。以为之师以纠群后。则一州之地而十二侯已多矣。更别有许多小国之属于大国者耶。
周之时九州千八百国。
外迫四海。咸建五长。传谓每方各建五人。此方字谓四方之方欤。
是。
方民之陷洪水也。其拯救之为时日急也。尧之使鲧而有九载不成何也。鲧之智必汩堙而止也。则于其经始也。尧之圣必先知其绩之可成与否。而其必待九载何也。
鲧非全然无功。亦有疏瀹之效。而大役非数年可了者。则尧之姑任之可也。况未得其贤于鲧者乎。及舜之摄而鲧果方命而不遵教。堙汩而圮族。于是举禹而代之。禹因鲧之功而修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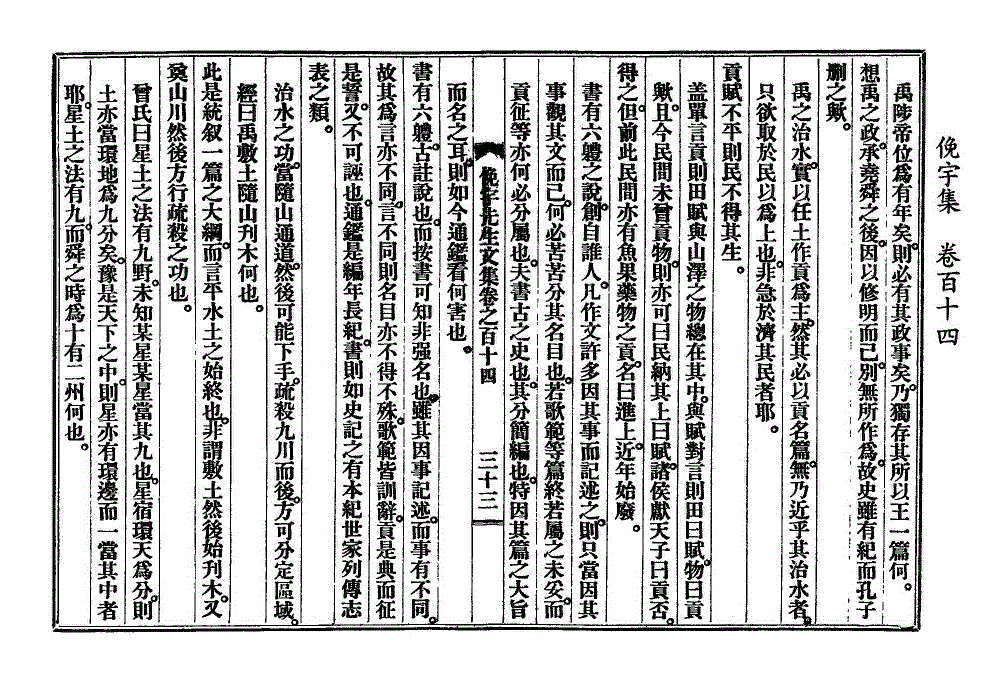 禹陟帝位为有年矣。则必有其政事矣。乃独存其所以王一篇何。
禹陟帝位为有年矣。则必有其政事矣。乃独存其所以王一篇何。想禹之政。承尧舜之后。因以修明而已。别无所作为。故史虽有纪而孔子删之欤。
禹之治水。实以任土作贡为主。然其必以贡名篇。无乃近乎其治水者。只欲取于民以为上也。非急于济其民者耶。
贡赋不平则民不得其生。
盖单言贡则田赋与山泽之物总在其中。与赋对言则田曰赋。物曰贡欤。且今民间未曾贡物。则亦可曰民纳其上曰赋。诸侯献天子曰贡否。
得之。但前此民间亦有鱼果药物之贡。名曰进上。近年始废。
书有六体之说。创自谁人。凡作文许多因其事而记述之。则只当因其事观其文而已。何必苦苦分其名目也。若歌范等篇终若属之未妥。而贡征等亦何必分属也。夫书古之史也。其分简编也。特因其篇之大旨而名之耳。则如今通鉴看何害也。
书有六体。古注说也。而按书可知非强名也。虽其因事记述。而事有不同。故其为言亦不同。言不同则名目亦不得不殊。歌范皆训辞。贡是典而征是誓。又不可诬也。通鉴是编年长纪。书则如史记之有本纪世家列传志表之类。
治水之功。当随山通道。然后可能下手。疏杀九川而后。方可分定区域。经曰禹敷土随山刊木何也。
此是统叙一篇之大纲。而言平水土之始终也。非谓敷土然后始刊木。又奠山川然后方行疏杀之功也。
曾氏曰星土之法有九野。未知某星某星当其九也。星宿环天为分。则土亦当环地为九分矣。豫是天下之中。则星亦有环边而一当其中者耶。星土之法有九。而舜之时为十有二州何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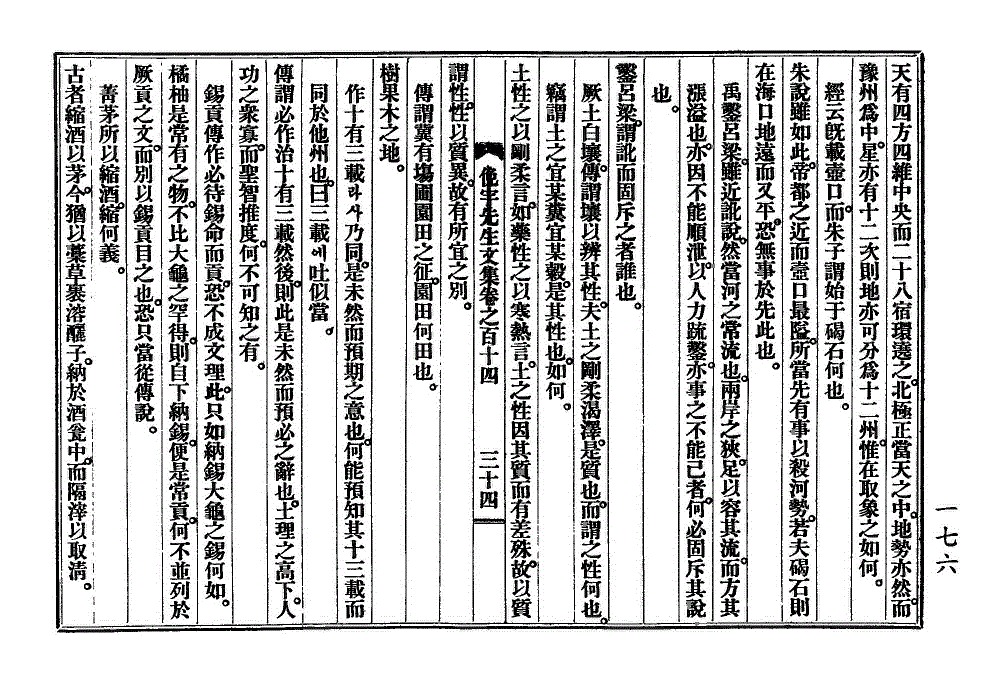 天有四方四维中央而二十八宿环绕之。北极正当天之中。地势亦然。而豫州为中。星亦有十二次则地亦可分为十二州。惟在取象之如何。
天有四方四维中央而二十八宿环绕之。北极正当天之中。地势亦然。而豫州为中。星亦有十二次则地亦可分为十二州。惟在取象之如何。经云既载壶口。而朱子谓始于碣石何也。
朱说虽如此。帝都之近而壸口最隘。所当先有事以杀河势。若夫碣石则在海口地远而又平。恐无事于先此也。
禹凿吕梁。虽近讹说。然当河之常流也。两岸之狭。足以容其流。而方其涨溢也。亦因不能顺泄。以人力疏凿。亦事之不能已者。何必固斥其说也。
凿吕梁。谓讹而固斥之者谁也。
厥土白壤。传谓壤以辨其性。夫土之刚柔渴泽。是质也。而谓之性何也。窃谓土之宜某粪宜某谷。是其性也。如何。
土性之以刚柔言。如药性之以寒热言。土之性因其质而有差殊。故以质谓性。性以质异。故有所宜之别。
传谓冀有场圃园田之征。园田何田也。
树果木之地。
作十有三载라사乃同。是未然而预期之意也。何能预知其十三载而同于他州也。曰三载에吐似当。
传谓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则此是未然而预必之辞也。土理之高下。人功之众寡。而圣智推度。何不可知之有。
锡贡传作必待锡命而贡。恐不成文理。此只如纳锡大龟之锡何如。
橘柚是常有之物。不比大龟之罕得。则自下纳锡。便是常贡。何不并列于厥贡之文。而别以锡贡目之也。恐只当从传说。
菁茅所以缩酒。缩何义。
古者缩酒以茅。今犹以藁草裹溶酾子。纳于酒瓮中。而隔滓以取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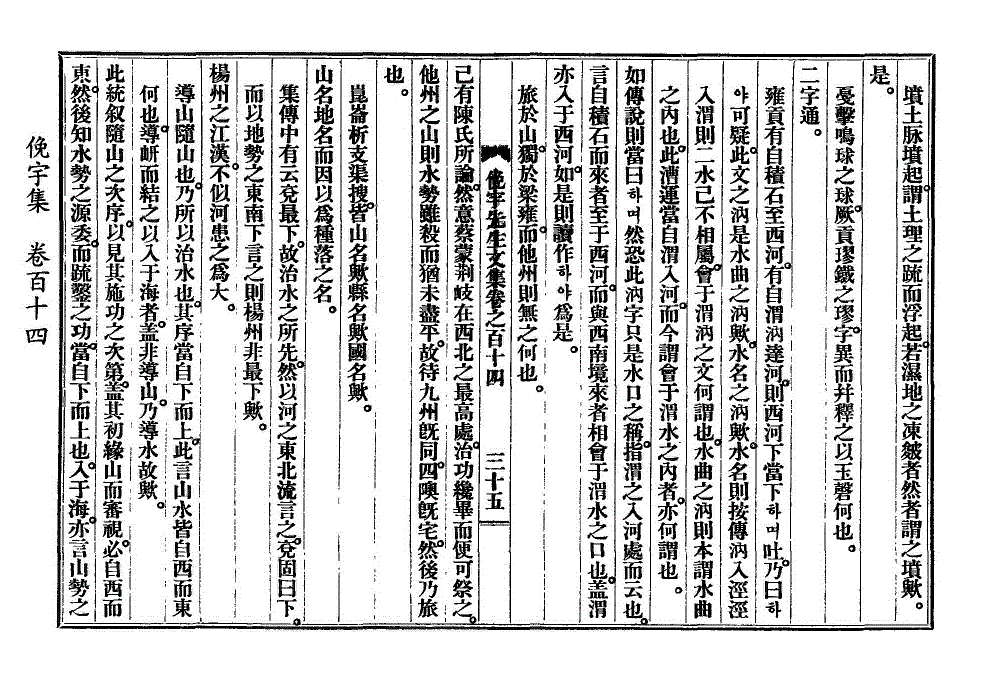 坟土脉坟起。谓土理之疏而浮起。若湿地之冻皴者然者谓之坟欤。
坟土脉坟起。谓土理之疏而浮起。若湿地之冻皴者然者谓之坟欤。是。
戛击鸣球之球。厥贡璆铁之璆。字异而并释之以玉磬何也。
二字通。
雍贡有自积石至西河。有自渭汭达河。则西河下当下하며吐。乃曰하야可疑。此文之汭是水曲之汭欤。水名之汭欤。水名则按传汭入泾泾入渭则二水已不相属。会于渭汭之文何谓也。水曲之汭则本谓水曲之内也。此漕运当自渭入河。而今谓会于渭水之内者。亦何谓也。
如传说则当曰하며然恐此汭字只是水口之称。指渭之入河处而云也。言自积石而来者至于西河。而与西南境来者相会于渭水之口也。盖渭亦入于西河。如是则读作하야为是。
旅于山。独于梁雍。而他州则无之何也。
已有陈氏所论。然意蔡蒙荆岐在西北之最高处。治功才毕而便可祭之。他州之山则水势虽杀而犹未尽平。故待九州既同。四隩既宅。然后乃旅也。
昆崙析支渠搜。皆山名欤县名欤国名欤。
山名地名而因以为种落之名。
集传中有云兖最下。故治水之所先。然以河之东北流言之。兖固曰下。而以地势之东南下言之则杨(一作扬)州非最下欤。
杨(一作扬)州之江汉。不似河患之为大。
导山随山也。乃所以治水也。其序当自下而上。此言山水皆自西而东何也。导岍而结之以入于海者。盖非导山。乃导水故欤。
此统叙随山之次序。以见其施功之次第。盖其初缘山而审视。必自西而东。然后知水势之源委。而疏凿之功。当自下而上也。入于海。亦言山势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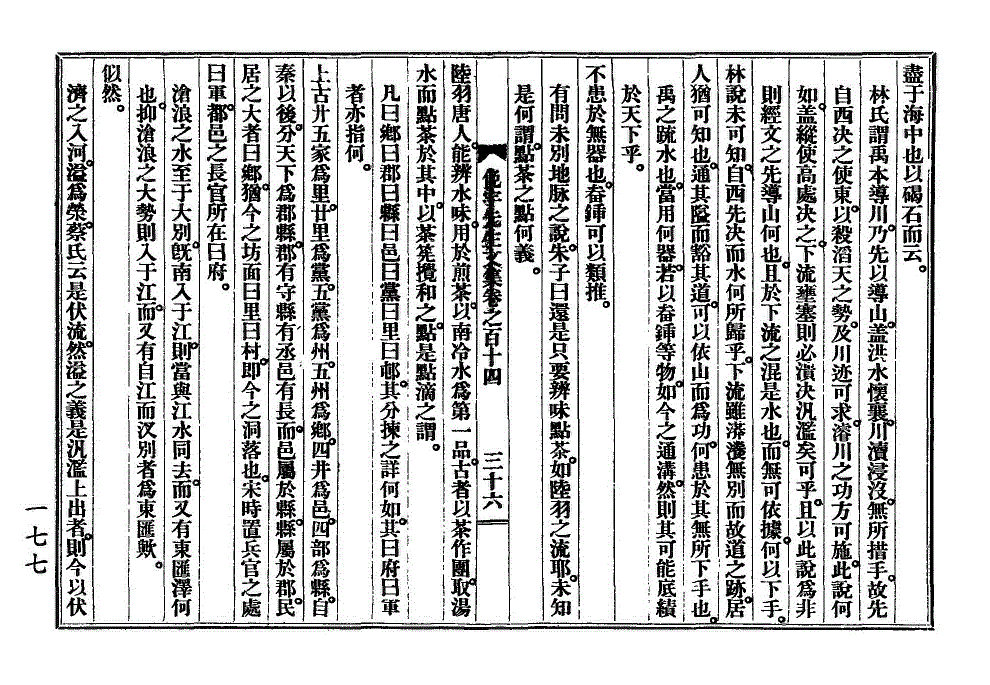 尽于海中也以碣石而云。
尽于海中也以碣石而云。林氏谓禹本导川。乃先以导山。盖洪水怀襄。川渎浸没。无所措手。故先自西决之使东。以杀滔天之势。及川迹可求。浚川之功方可施。此说何如。盖纵使高处决之。下流壅塞则必溃决汎滥矣可乎。且以此说为非则经文之先导山何也。且于下流之混是水也。而无可依据。何以下手。
林说未可知。自西先决而水何所归乎。下流虽漭瀁无别而故道之迹。居人犹可知也。通其隘而豁其道。可以依山而为功。何患于其无所下手也。
禹之疏水也。当用何器。若以畚锸等物。如今之通沟。然则其可能底绩于天下乎。
不患于无器也。畚锸可以类推。
有问未别地脉之说。朱子曰还是只要辨味点茶。如陆羽之流耶。未知是何谓。点茶之点何义。
陆羽唐人。能辨水味。用于煎茶。以南冷水为第一品。古者以茶作团。取汤水而点茶于其中。以茶筅搅和之。点是点滴之谓。
凡曰乡曰郡曰县曰邑曰党曰里曰村。其分拣之详何如。其曰府曰军者亦指何。
上古廿五家为里。廿里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四井为邑。四部为县。自秦以后。分天下为郡县。郡有守县有丞邑有长。而邑属于县。县属于郡。民居之大者曰乡。犹今之坊面曰里曰村。即今之洞落也。宋时置兵官之处曰军。都邑之长官所在曰府。
沧浪之水至于大别。既南入于江。则当与江水同去。而又有东汇泽何也。抑沧浪之大势则入于江。而又有自江而汊别者为东汇欤。
似然。
济之入河。溢为荥。蔡氏云是伏流。然溢之义是汎滥上出者。则今以伏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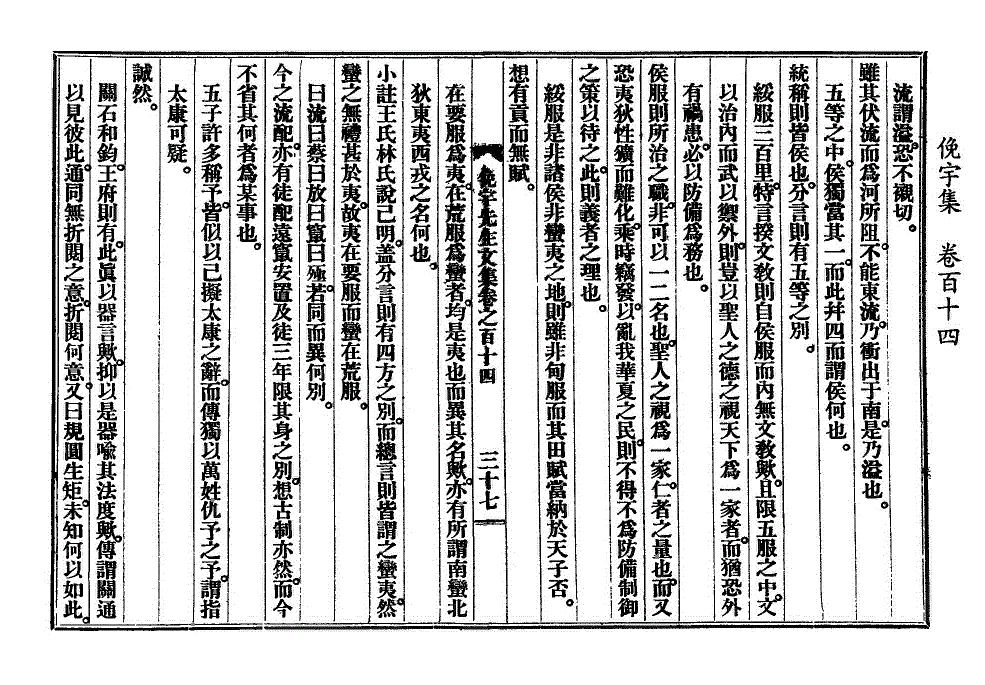 流谓溢。恐不衬切。
流谓溢。恐不衬切。虽其伏流而为河所阻。不能东流。乃冲出于南。是乃溢也。
五等之中。侯独当其一。而此并四而谓侯何也。
统称则皆侯也。分言则有五等之别。
绥服三百里。特言揆文教则自侯服而内无文教欤。且限五服之中。文以治内而武以御外。则岂以圣人之德之视天下为一家者。而犹恐外有祸患。必以防备为务也。
侯服则所治之职。非可以一二名也。圣人之视为一家。仁者之量也。而又恐夷狄性犷而难化。乘时窃发。以乱我华夏之民。则不得不为防备制御之策以待之。此则义者之理也。
绥服是非诸侯非蛮夷之地。则虽非甸服而其田赋当纳于天子否。
想有贡而无赋。
在要服为夷。在荒服为蛮者。均是夷也而异其名欤。亦有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名何也。
小注王氏林氏说已明。盖分言则有四方之别。而总言则皆谓之蛮夷。然蛮之无礼甚于夷。故夷在要服而蛮在荒服。
曰流曰蔡曰放曰窜曰殛。若同而异何别。
今之流配。亦有徒配远窜安置及徒三年限其身之别。想古制亦然。而今不省其何者为某事也。
五子许多称予。皆似以已拟太康之辞。而传独以万姓仇予之予。谓指太康可疑。
诚然。
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此真以器言欤。抑以是器喻其法度欤。传谓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折阅何意。又曰规圆生矩。未知何以如此。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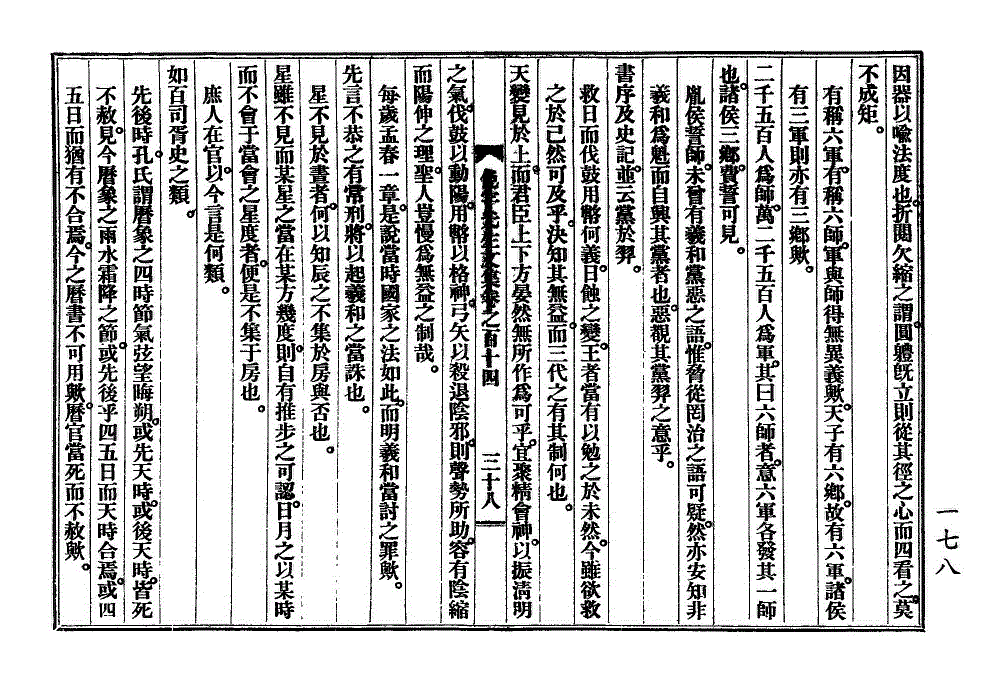 因器以喻法度也。折阅欠缩之谓。圆体既立则从其径之心而四看之。莫不成矩。
因器以喻法度也。折阅欠缩之谓。圆体既立则从其径之心而四看之。莫不成矩。有称六军。有称六师。军与师得无异义欤。天子有六乡。故有六军。诸侯有三军则亦有三乡欤。
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其曰六师者。意六军各发其一师也。诸侯三乡。费誓可见。
胤侯誓师。未曾有羲和党恶之语。惟胁从罔治之语可疑。然亦安知非羲和为魁而自兴其党者也。恶睹其党羿之意乎。
书序及史记。并云党于羿。
救日而伐鼓用币何义。日蚀之变。王者当有以勉之于未然。今虽欲救之于已然可及乎。决知其无益。而三代之有其制何也。
天变见于上。而君臣上下方晏然无所作为可乎。宜聚精会神。以振清明之气。伐鼓以动阳。用币以格神。弓矢以杀退阴邪。则声势所助。容有阴缩而阳伸之理。圣人岂慢为无益之制哉。
每岁孟春一章。是说当时国家之法如此。而明羲和当讨之罪欤。
先言不恭之有常刑。将以起羲和之当诛也。
星不见于昼者。何以知辰之不集于房与否也。
星虽不见而某星之当在某方几度。则自有推步之可认。日月之以某时而不会于当会之星度者。便是不集于房也。
庶人在官。以今言是何类。
如百司胥史之类。
先后时。孔氏谓历象之四时节气弦望晦朔。或先天时。或后天时。皆死不赦。见今历象之雨水霜降之节。或先后乎四五日而天时合焉。或四五日而犹有不合焉。今之历书不可用欤。历官当死而不赦欤。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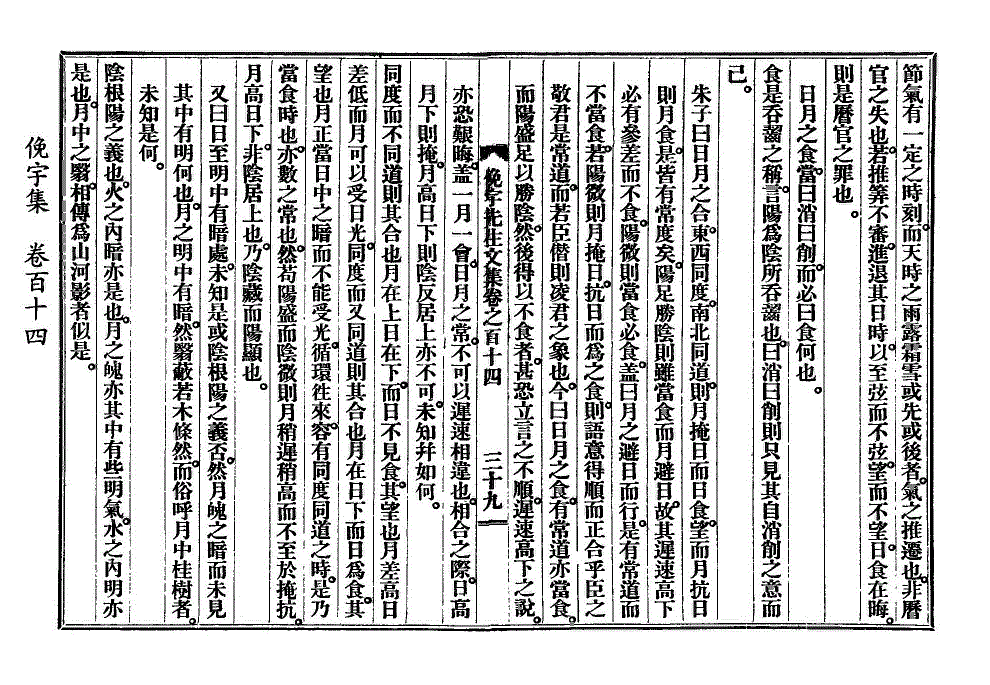 节气有一定之时刻。而天时之雨露霜雪或先或后者。气之推迁也。非历官之失也。若推算不审。进退其日时。以至弦而不弦。望而不望。日食在晦。则是历官之罪也。
节气有一定之时刻。而天时之雨露霜雪或先或后者。气之推迁也。非历官之失也。若推算不审。进退其日时。以至弦而不弦。望而不望。日食在晦。则是历官之罪也。日月之食。当曰消曰削。而必曰食何也。
食是吞齧之称。言阳为阴所吞齧也。曰消曰削则只见其自消削之意而已。
朱子曰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月抗日则月食。是皆有常度矣。阳足胜阴则虽当食而月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食。阳微则当食必食。盖曰月之避日而行。是有常道而不当食。若阳微则月掩日。抗日而为之食。则语意得顺而正合乎臣之敬君是常道。而若臣僭则凌君之象也。今曰日月之食。有常道亦当食。而阳盛足以胜阴。然后得以不食者。甚恐立言之不顺。迟速高下之说。亦恐艰晦。盖一月一会。日月之常。不可以迟速相违也。相合之际。日高月下则掩。月高日下则阴反居上亦不可。未知并如何。
同度而不同道则其合也月在上日在下。而日不见食。其望也月差高日差低而月可以受日光。同度而又同道则其合也月在日下而日为食。其望也月正当日中之暗而不能受光。循环往来。容有同度同道之时。是乃当食时也。亦数之常也。然苟阳盛而阴微则月稍迟稍高而不至于掩抗。月高日下。非阴居上也。乃阴藏而阳显也。
又曰日至明中有暗处。未知是或阴根阳之义否。然月魄之暗而未见其中有明何也。月之明中有暗。然翳蔽若木条然。而俗呼月中桂树者。未知是何。
阴根阳之义也。火之内暗亦是也。月之魄亦其中有些明气。水之内明亦是也。月中之翳。相传为山河影者似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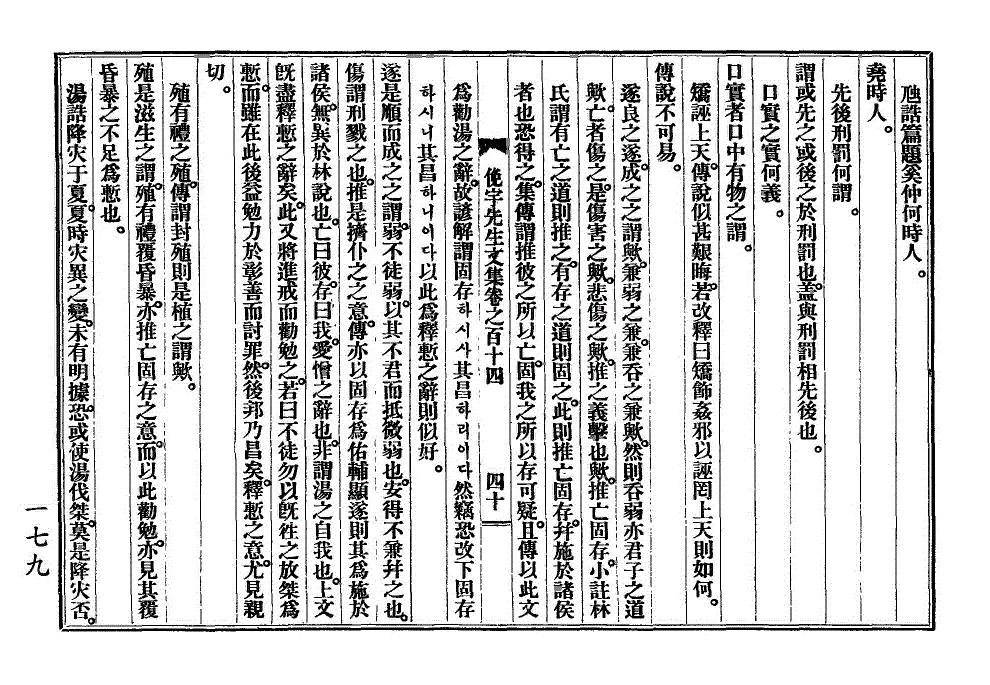 虺诰篇题奚仲何时人。
虺诰篇题奚仲何时人。尧时人。
先后刑罚何谓。
谓或先之或后之于刑罚也。盖与刑罚相先后也。
口实之实何义。
口实者口中有物之谓。
矫诬上天。传说似甚艰晦。若改释曰矫饰奸邪以诬罔上天则如何。
传说不可易。
遂良之遂。成之之谓欤。兼弱之兼。兼吞之兼欤。然则吞弱亦君子之道欤。亡者伤之。是伤害之欤。悲伤之欤。推之义击也欤。推亡固存。小注林氏谓有亡之道则推之。有存之道则固之。此则推亡固存。并施于诸侯者也恐得之。集传谓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可疑。且传以此文为劝汤之辞。故谚解谓固存하시사其昌하리이다然窃恐改下固存하시니其昌하니이다以此为释惭之辞则似好。
遂是顺而成之之谓。弱不徒弱。以其不君而抵微弱也。安得不兼并之也。伤谓形戮之也。推是挤仆之之意。传亦以固存为佑辅显遂则其为施于诸侯。无异于林说也。亡曰彼。存曰我。爱憎之辞也。非谓汤之自我也。上文既尽释惭之辞矣。此又将进戒而劝勉之。若曰不徒勿以既往之放桀为惭。而虽在此后益勉力于彰善而讨罪。然后邦乃昌矣。释惭之意。尤见亲切。
殖有礼之殖。传谓封殖则是植之谓欤。
殖是滋生之谓。殖有礼覆昏暴。亦推亡固存之意。而以此劝勉。亦见其覆昏暴之不足为惭也。
汤诰降灾于夏。夏时灾异之变。未有明据。恐或使汤伐桀。莫是降灾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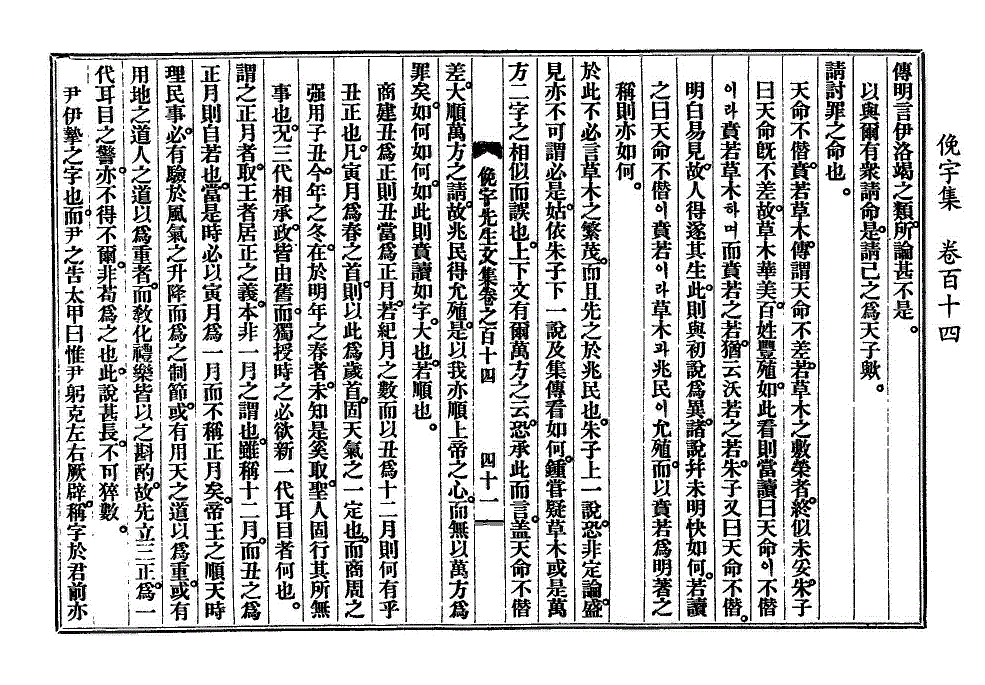 传明言伊洛竭之类。所论甚不是。
传明言伊洛竭之类。所论甚不是。以与尔有众请命。是请己之为天子欤。
请讨罪之命也。
天命不僭。贲若草木。传谓天命不差。若草木之敷荣者。终似未妥。朱子曰天命既不差。故草木华美。百姓丰殖。如此看则当读曰天命이不僭이라贲若草木하며而贲若之若。犹云沃若之若。朱子又曰天命不僭。明白易见。故人得遂其生。此则与初说为异。诸说并未明快如何。若读之曰天命不僭이贲若이라草木과兆民이允殖。而以贲若为明著之称则亦如何。
于此不必言草木之繁茂。而且先之于兆民也。朱子上一说。恐非定论。盛见亦不可谓必是。姑依朱子下一说及集传看如何。钟尝疑草木或是万方二字之相似而误也。上下文有尔万方之云。恐承此而言。盖天命不僭差。大顺万方之请。故兆民得允殖。是以我亦顺上帝之心。而无以万方为罪矣。如何如何。如此则贲读如字。大也。若顺也。
商建丑为正则丑当为正月。若纪月之数而以丑为十二月则何有乎丑正也。凡寅月为春之首。则以此为岁首。固天气之一定也。而商周之强用子丑。今年之冬。在于明年之春者。未知是奚取。圣人固行其所无事也。况三代相承。政皆由旧。而独授时之必欲新一代耳目者何也。
谓之正月者。取王者居正之义。本非一月之谓也。虽称十二月。而丑之为正月则自若也。当是时必以寅月为一月而不称正月矣。帝王之顺天时理民事。必有验于风气之升降而为之制节。或有用天之道以为重。或有用地之道人之道以为重者。而教化礼乐皆以之斟酌。故先立三正。为一代耳目之警。亦不得不尔。非苟为之也。此说甚长。不可猝数。
尹伊挚之字也。而尹之告太甲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称字于君前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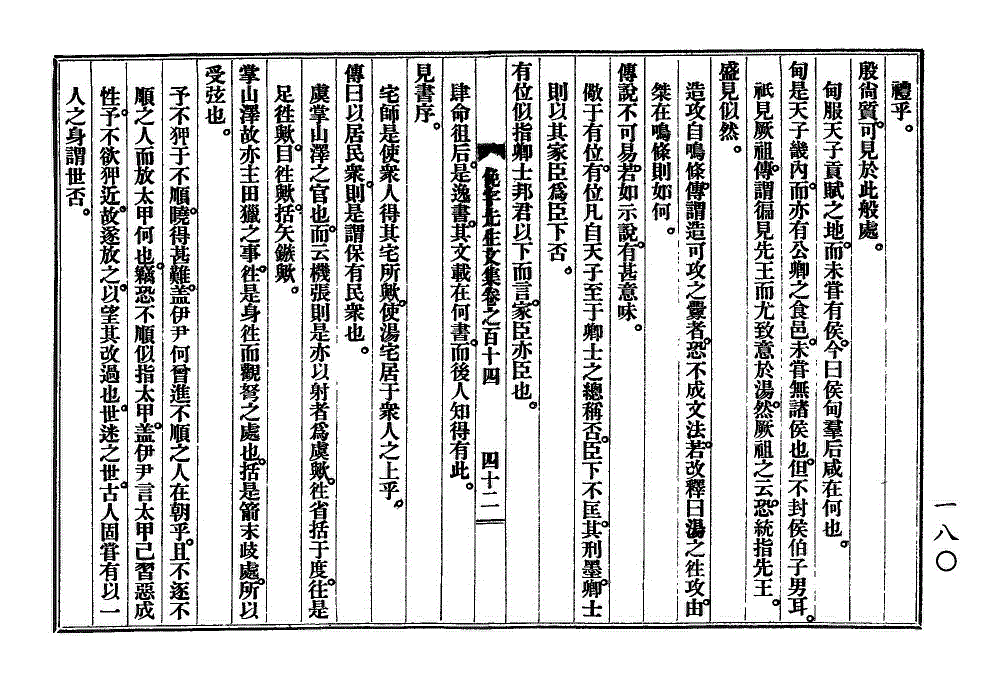 礼乎。
礼乎。殷尚质。可见于此般处。
甸服天子贡赋之地。而未尝有侯。今曰侯甸群后咸在何也。
甸是天子畿内。而亦有公卿之食邑。未尝无诸侯也。但不封侯伯子男耳。
祇见厥祖。传谓遍见先王而尤致意于汤。然厥祖之云。恐统指先王。
盛见似然。
造攻自鸣条。传谓造可攻之衅者。恐不成文法。若改释曰汤之往攻。由桀在鸣条则如何。
传说不可易。若如示说。有甚意味。
儆于有位。有位凡自天子至于卿士之总称否。臣下不匡。其刑墨。卿士则以其家臣为臣下否。
有位似指卿士邦君以下而言。家臣亦臣也。
肆命徂后。是逸书。其文载在何书。而后人知得有此。
见书序。
宅师是使众人得其宅所欤。使汤宅居于众人之上乎。
传曰以居民众。则是谓保有民众也。
虞掌山泽之官也。而云机张则是亦以射者为虞欤。往省括于度。往是足往欤。目往欤。括矢镞欤。
掌山泽故亦主田猎之事。往是身往而观弩之处也。括是箭末歧处。所以受弦也。
予不狎于不顺。晓得甚难。盖伊尹何曾进不顺之人在朝乎。且不逐不顺之人而放太甲何也。窃恐不顺似指太甲。盖伊尹言太甲已习恶成性。予不欲狎近。故遂放之。以望其改过也。世迷之世。古人固尝有以一人之身谓世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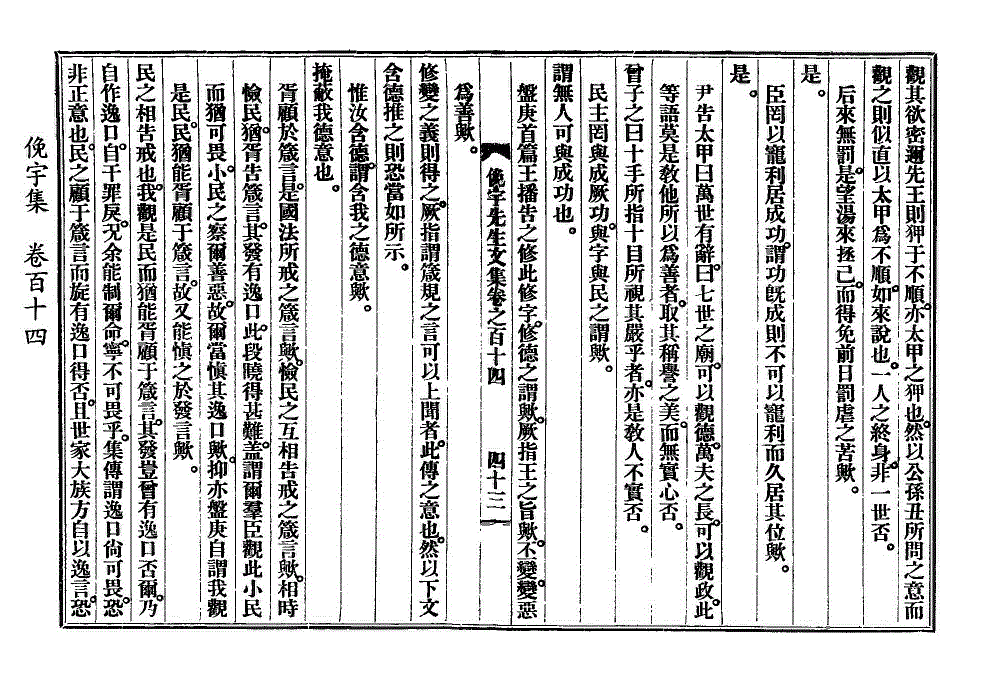 观其欲密迩先王则狎于不顺。亦太甲之狎也。然以公孙丑所问之意而观之则似直以太甲为不顺。如来说也。一人之终身。非一世否。
观其欲密迩先王则狎于不顺。亦太甲之狎也。然以公孙丑所问之意而观之则似直以太甲为不顺。如来说也。一人之终身。非一世否。后来无罚。是望汤来拯己。而得免前日罚虐之苦欤。
是。
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谓功既成则不可以宠利而久居其位欤。
是。
尹告太甲曰万世有辞。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此等语莫是教他所以为善者。取其称誉之美。而无实心否。
曾子之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其严乎者。亦是教人不实否。
民主罔与成厥功。与字与民之谓欤。
谓无人可与成功也。
盘庚首篇王播告之修此修字。修德之谓欤。厥指王之旨欤。丕变。变恶为善欤。
修变之义则得之。厥指谓箴规之言可以上闻者。此传之意也。然以下文含德推之则恐当如所示。
惟汝含德。谓含我之德意欤。
掩蔽我德意也。
胥顾于箴言。是国法所戒之箴言欤。憸民之互相告戒之箴言欤。相时憸民。犹胥告箴言。其发有逸口。此段晓得甚难。盖谓尔群臣观此小民而犹可畏。小民之察尔善恶。故尔当慎其逸口欤。抑亦盘庚自谓我观是民。民犹能胥顾于箴言。故又能慎之于发言欤。
民之相告戒也。我观是民而犹能胥顾于箴言。其发岂曾有逸口否尔。乃自作逸口。自干罪戾。况余能制尔命。宁不可畏乎。集传谓逸口尚可畏。恐非正意也。民之顾于箴言而旋有逸口得否。且世家大族方自以逸言。恐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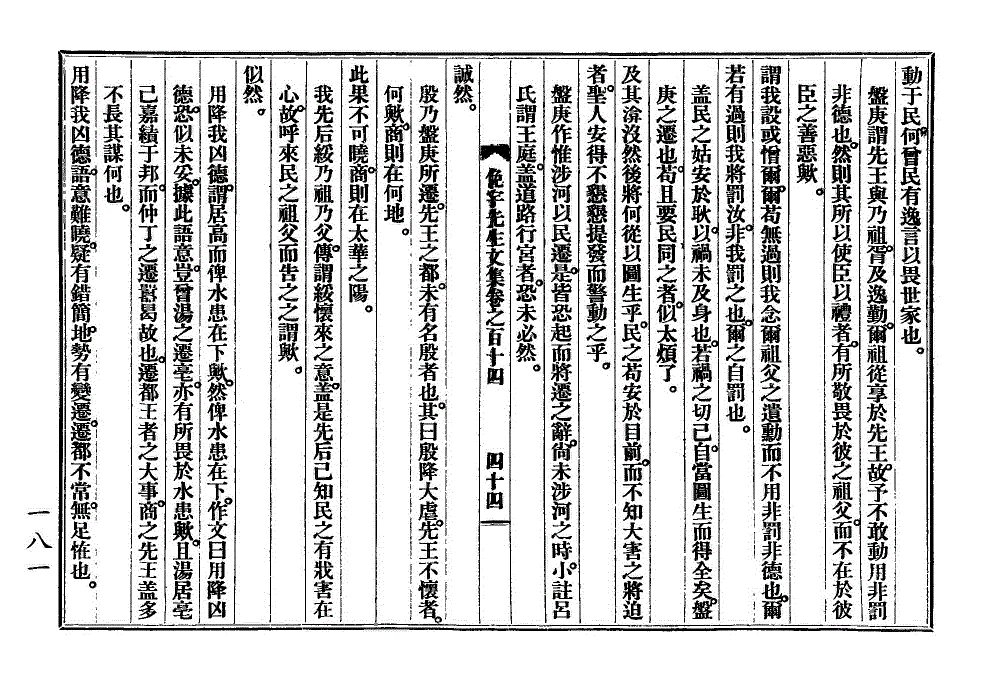 动于民。何曾民有逸言以畏世家也。
动于民。何曾民有逸言以畏世家也。盘庚谓先王与乃祖。胥及逸勤。尔祖从享于先王。故予不敢动用非罚非德也。然则其所以使臣以礼者。有所敬畏于彼之祖父。而不在于彼臣之善恶欤。
谓我设或憎尔。尔苟无过则我念尔祖父之遗勋而不用非罚非德也。尔若有过则我将罚汝。非我罚之也。尔之自罚也。
盖民之姑安于耿。以祸未及身也。若祸之切己。自当图生而得全矣。盘庚之迁也。苟且要民同之者。似太烦了。
及其渰没然后将何从以图生乎。民之苟安于目前。而不知大害之将迫者。圣人安得不恳恳提发而警动之乎。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是皆恐起而将迁之辞。尚未涉河之时。小注吕氏谓王庭。盖道路行宫者。恐未必然。
诚然。
殷乃盘庚所迁。先王之都。未有名殷者也。其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怀者。何欤。商则在何地。
此果不可晓。商则在太华之阳。
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传谓绥怀来之意。盖是先后已知民之有戕害在心。故呼来民之祖父而告之之谓欤。
似然。
用降我凶德。谓居高而俾水患在下欤。然俾水患在下。作文曰用降凶德。恐似未妥。据此语意。岂曾汤之迁亳。亦有所畏于水患欤。且汤居亳已嘉积于邦。而仲丁之迁嚣曷故也。迁都王者之大事。商之先王盖多不长其谋何也。
用降我凶德。语意难晓。疑有错简。地势有变迁。迁都不常。无足怪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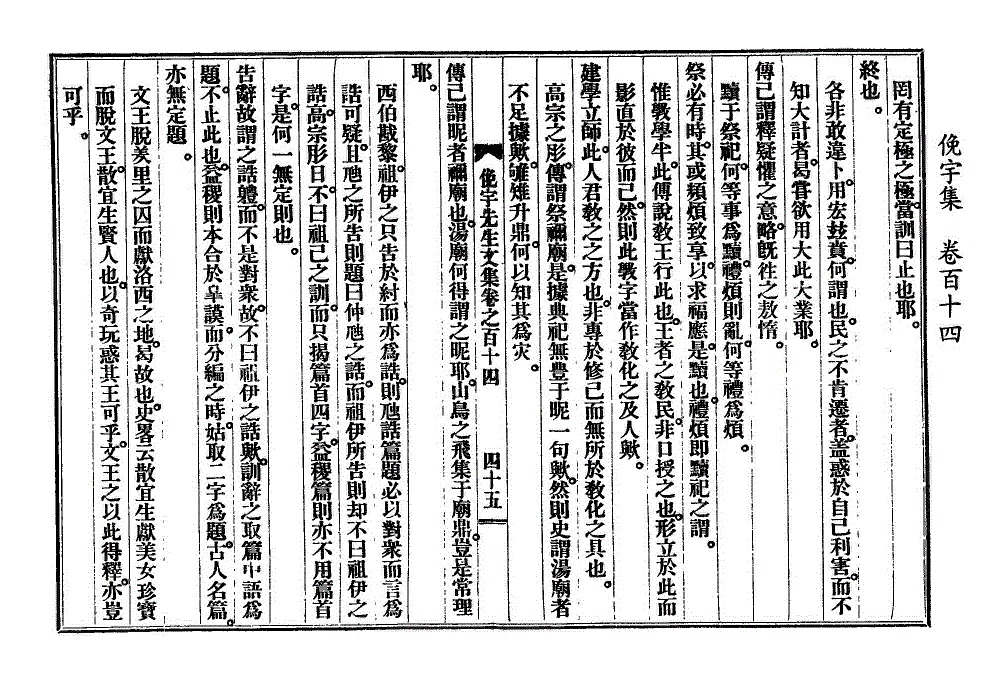 罔有定极之极。当训曰止也耶。
罔有定极之极。当训曰止也耶。终也。
各非敢违卜。用宏玆贲。何谓也。民之不肯迁者。盖惑于自己利害。而不知大计者。曷尝欲用大此大业耶。
传已谓释疑惧之意。略既往之敖惰。
黩于祭祀。何等事为黩。礼烦则乱。何等礼为烦。
祭必有时。其或频烦致享。以求福应。是黩也。礼烦即黩祀之谓。
惟敩学半。此傅说教王行此也。王者之教民。非口授之也。形立于此而影直于彼而已。然则此敩字当作教化之及人欤。
建学立师。此人君教之之方也。非专于修己而无所于教化之具也。
高宗之肜。传谓祭祢庙。是据典祀无礼于昵一句欤。然则史谓汤庙者不足据欤。雊雉升鼎。何以知其为灾。
传已谓昵者祢庙也。汤庙何得谓之昵耶。山鸟之飞集于庙鼎。岂是常理耶。
西伯戡黎。祖伊之只告于纣而亦为诰。则虺诰篇题必以对众而言为诰可疑。且虺之所告则题曰仲虺之诰。而祖伊所告则却不曰祖伊之诰。高宗肜日。不曰祖已之训。而只揭篇首四字。益稷篇则亦不用篇首字。是何一无定则也。
告辞故谓之诰体。而不是对众。故不曰祖伊之诰欤。训辞之取篇中语为题。不止此也。益稷则本合于皋谟。而分编之时。姑取二字为题。古人名篇。亦无定题。
文王脱羑里之囚而献洛西之地。曷故也。史略云散宜生献美女珍宝而脱文王。散宜生贤人也。以奇玩惑其王可乎。文王之以此得释。亦岂可乎。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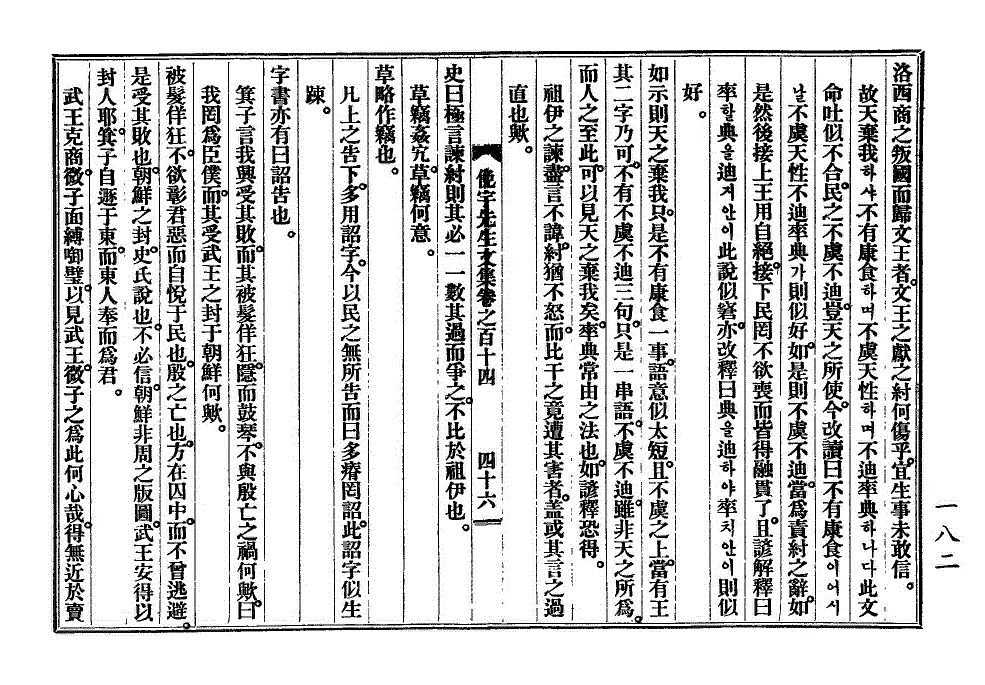 洛西商之叛国而归文王者。文王之献之纣何伤乎。宜生事未敢信。
洛西商之叛国而归文王者。文王之献之纣何伤乎。宜生事未敢信。故天弃我하샤不有康食하며不虞天性하며不迪率典하나다此文命吐似不合。民之不虞不迪。岂天之所使。今改读曰不有康食이어시날不虞天性不迪率典가则似好。如是则不虞不迪。当为责纣之辞。如是然后接上王用自绝。接下民罔不欲丧而皆得融贯了。且谚解释曰率할典을迪지안이此说似窘。亦改释曰典을迪하야率치안이则似好。
如示则天之弃我。只是不有康食一事。语意似太短。且不虞之上。当有王其二字乃可。不有不虞不迪三句。只是一串语。不虞不迪。虽非天之所为。而人之至此。可以见天之弃我矣。率典常由之法也。如谚释恐得。
祖伊之谏。尽言不讳。纣犹不怒。而比干之竟遭其害者。盖或其言之过直也欤。
史曰极言谏纣则其必一一数其过而争之。不比于祖伊也。
草窃奸宄。草窃何意。
草略作窃也。
凡上之告下。多用诏字。今以民之无所告而曰多瘠罔诏。此诏字似生疏。
字书亦有曰诏告也。
箕子言我兴受其败。而其被发佯狂。隐而鼓琴。不与殷亡之祸何欤。曰我罔为臣仆。而其受武王之封于朝鲜何欤。
被发佯狂。不欲彰君恶而自悦于民也。殷之亡也。方在囚中。而不曾逃避。是受其败也。朝鲜之封。史氏说也。不必信。朝鲜非周之版图。武王安得以封人耶。箕子自遁于东。而东人奉而为君。
武王克商。微子面缚衔璧。以见武王。微子之为此何心哉。得无近于卖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百十四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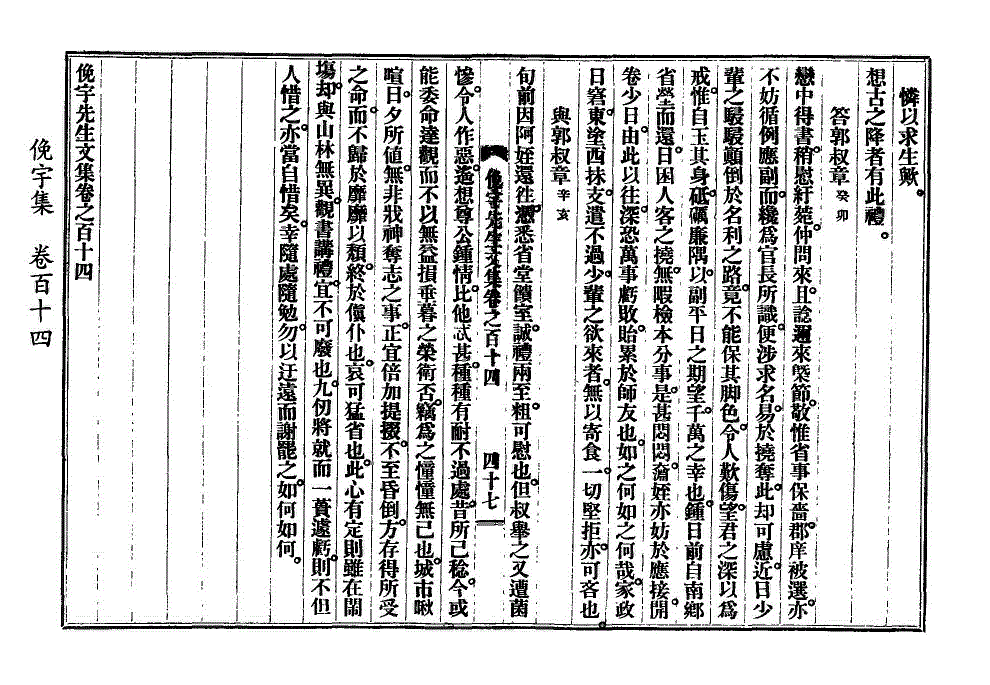 怜以求生欤。
怜以求生欤。想古之降者有此礼。
答郭叔章(癸卯)
恋中得书。稍慰纡菀。仲问来。且谂迩来槩节。敬惟省事保啬。郡庠被选。亦不妨循例应副。而才为官长所识。便涉求名。易于挠夺。此切可虑。近日少辈之骎骎颠倒于名利之路。竟不能保其脚色。令人叹伤。望君之深以为戒。惟自玉其身。砥砺廉隅。以副平日之期望。千万之幸也。钟日前自南乡省茔而还。日困人客之挠。无暇检本分事。是甚闷闷。奫侄亦妨于应接。开卷少日。由此以往。深恐万事亏败。贻累于师友也。如之何如之何哉。家政日窘。东涂西抺。支遣不过。少辈之欲来者。无以寄食。一切坚拒。亦可吝也。
与郭叔章(辛亥)
旬前因阿侄还往。凭悉省堂馈室。诚礼两至。粗可慰也。但叔举之又遭菌惨。令人作恶。遥想尊公钟情。比他忒甚。种种有耐不过处。昔所已稔。今或能委命达观而不以无益损垂暮之荣卫否。窃为之憧憧无已也。城市啾喧。日夕所值。无非戕神夺志之事。正宜倍加提掇。不至昏倒。方存得所受之命。而不归于靡靡以颓。终于颠仆也。哀可猛省也。此心有定则虽在闹场。却与山林无异。观书讲礼。宜不可废也。九仞将就而一蒉遽亏。则不但人惜之。亦当自惜矣。幸随处随勉。勿以迂远而谢罢之。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