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书
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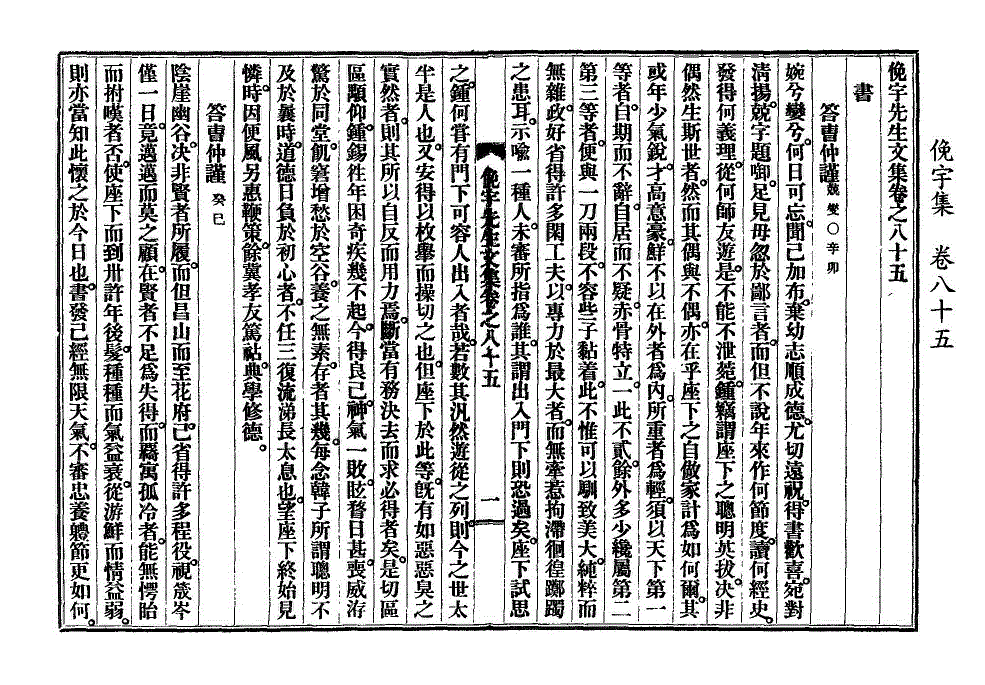 答曹仲谨(兢燮○辛卯)
答曹仲谨(兢燮○辛卯)婉兮娈兮。何日可忘。闻已加布。弃幼志顺成德。尤切远祝。得书欢喜。宛对清扬。兢字题衔。足见毋忽于鄙言者。而但不说年来作何节度。读何经史。发得何义理。从何师友游。是不能不泄菀。钟窃谓座下之聪明英拔。决非偶然生斯世者。然而其偶与不偶。亦在乎座下之自做家计为如何尔。其或年少气锐。才高意豪。鲜不以在外者为内。所重者为轻。须以天下第一等者。自期而不辞。自居而不疑。赤骨特立。一此不贰。馀外多少才属第二第三等者。便与一刀两段。不容些子黏着。此不惟可以驯致美大。纯粹而无杂。政好省得许多闲工夫。以专力于最大者。而无牵惹拘滞徊徨踯躅之患耳。示喻一种人。未审所指为谁。其谓出入门下则恐过矣。座下试思之。钟何尝有门下可容人出入者哉。若数其汎然游从之列。则今之世太半是人也。又安得以枚举而操切之也。但座下于此等。既有如恶恶臭之实然者。则其所以自反而用力焉。断当有务决去而求必得者矣。是切区区颙仰。钟锡往年困奇疾几不起。今得良已。神气一败。眩瞀日甚。丧威荐惊于同堂。饥窘增愁于空谷。养之无素。存者其几。每念韩子所谓聪明不及于曩时。道德日负于初心者。不任三复流涕长太息也。望座下终始见怜。时因便风另惠鞭策。馀冀孝友笃祜。典学修德。
答曹仲谨(癸巳)
阴崖幽谷。决非贤者所履。而但昌山而至花府。已省得许多程役。视筬岑仅一日。竟迈迈而莫之顾。在贤者不足为失得。而羁寓孤冷者。能无愕眙而拊叹者否。使座下而到卅许年后。发种种而气益衰。从游鲜而情益弱。则亦当知此怀之于今日也。书发已经无限天气。不审忠养体节更如何。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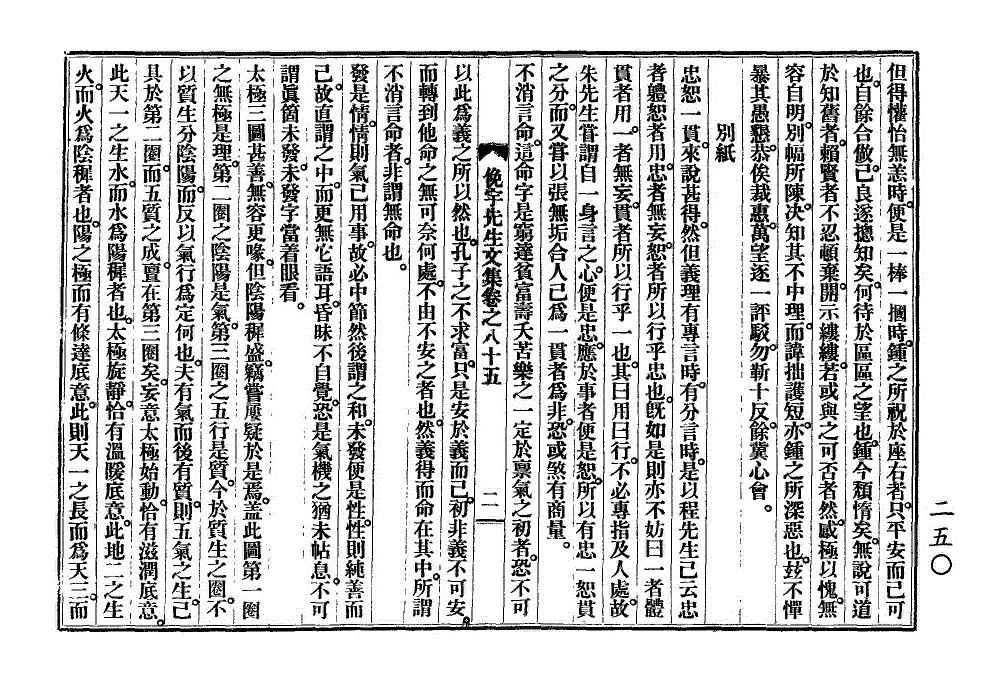 但得欢怡无恙时。便是一棒一掴时。钟之所祝于座右者。只平安而已可也。自馀合做。已良遂总知矣。何待于区区之望也。钟今颓惰矣。无说可道于知旧者。赖贤者不忍顿弃。开示缕缕。若或与之可否者然。感极以愧。无容自明。别幅所陈。决知其不中理。而讳拙护短。亦钟之所深恶也。玆不惮暴其愚恳。恭俟裁惠。万望逐一评驳。勿靳十反。馀冀心会。
但得欢怡无恙时。便是一棒一掴时。钟之所祝于座右者。只平安而已可也。自馀合做。已良遂总知矣。何待于区区之望也。钟今颓惰矣。无说可道于知旧者。赖贤者不忍顿弃。开示缕缕。若或与之可否者然。感极以愧。无容自明。别幅所陈。决知其不中理。而讳拙护短。亦钟之所深恶也。玆不惮暴其愚恳。恭俟裁惠。万望逐一评驳。勿靳十反。馀冀心会。别纸
忠恕一贯。来说甚得。然但义理有专言时。有分言时。是以程先生已云忠者体恕者用。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既如是则亦不妨曰一者体贯者用。一者无妄。贯者所以行乎一也。其曰用曰行。不必专指及人处。故朱先生尝谓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应于事者便是恕。所以有忠一恕贯之分。而又尝以张无垢合人已为一贯者为非。恐或煞有商量。
不消言命。这命字是穷达贫富寿夭苦乐之一定于禀气之初者。恐不可以此为义之所以然也。孔子之不求富。只是安于义而已。初非义不可安。而转到他命之无可奈何处。不由不安之者也。然义得而命在其中。所谓不消言命者。非谓无命也。
发是情。情则气已用事。故必中节然后谓之和。未发便是性。性则纯善而已。故直谓之中。而更无它语耳。昏昧不自觉。恐是气机之犹未帖息。不可谓真个未发。未发字当着眼看。
太极三图甚善。无容更喙。但阴阳稚盛。窃尝屡疑于是焉。盖此图第一圈之无极是理。第二圈之阴阳是气。第三圈之五行是质。今于质生之圈。不以质生分阴阳。而反以气行为定何也。夫有气而后有质。则五气之生。已具于第二圈。而五质之成。亶在第三圈矣。妄意太极始动。恰有滋润底意。此天一之生水。而水为阳稚者也。太极旋静。恰有温暖底意。此地二之生火。而火为阴稚者也。阳(一作动)之极而有条达底意。此则天一之长而为天三。而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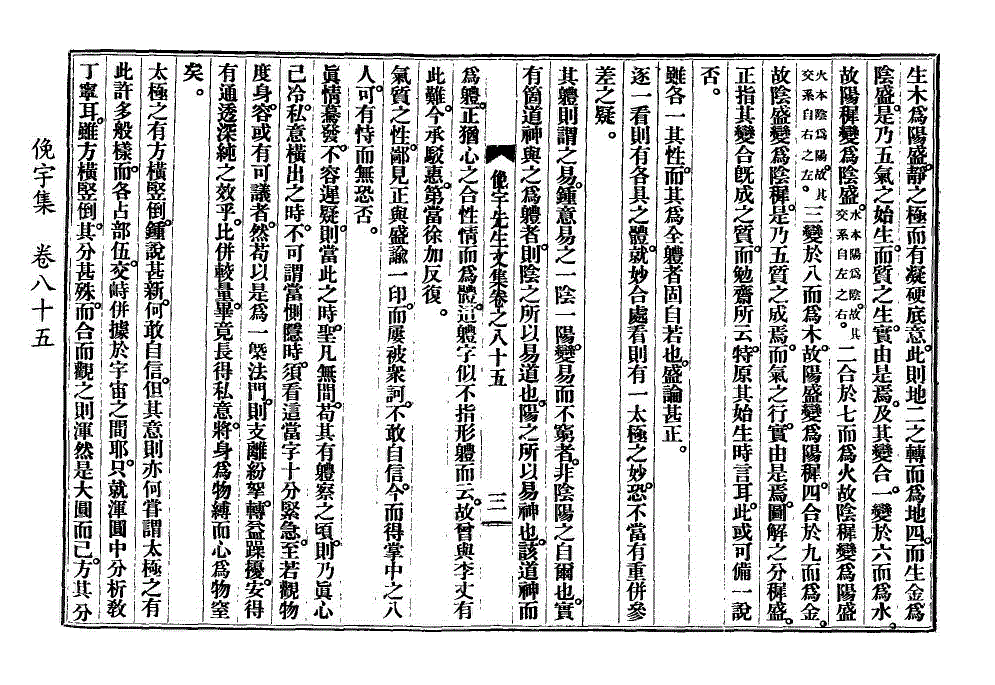 生木为阳盛。静之极而有凝硬底意。此则地二之转而为地四。而生金为阴盛。是乃五气之始生。而质之生。实由是焉。及其变合。一变于六而为水。故阳稚变为阴盛。(水本阳为阴。故其交系自左之右。)二合于七而为火故阴稚变为阳盛(火本阴为阳。故其交系自右之左。)三变于八而为木。故阳盛变为阳稚。四合于九而为金。故阴盛变为阴稚。是乃五质之成焉。而气之行。实由是焉。图解之分稚盛。正指其变合既成之质。而勉斋所云。特原其始生时言耳。此或可备一说否。
生木为阳盛。静之极而有凝硬底意。此则地二之转而为地四。而生金为阴盛。是乃五气之始生。而质之生。实由是焉。及其变合。一变于六而为水。故阳稚变为阴盛。(水本阳为阴。故其交系自左之右。)二合于七而为火故阴稚变为阳盛(火本阴为阳。故其交系自右之左。)三变于八而为木。故阳盛变为阳稚。四合于九而为金。故阴盛变为阴稚。是乃五质之成焉。而气之行。实由是焉。图解之分稚盛。正指其变合既成之质。而勉斋所云。特原其始生时言耳。此或可备一说否。虽各一其性。而其为全体者固自若也。盛论甚正。
逐一看则有各具之体。就妙合处看则有一太极之妙。恐不当有重并参差之疑。
其体则谓之易。钟意易之一阴一阳。变易而不穷者。非阴阳之自尔也。实有个道神与之为体者。则阴之所以易道也。阳之所以易神也。该道神而为体。正犹心之合性情而为体。这体字似不指形体而云。故曾与李丈有此难。今承驳惠。第当徐加反复。
气质之性。鄙见正与盛谕一印。而屡被众诃。不敢自信。今而得掌中之八人。可有恃而无恐否。
真情蓦发。不容迟疑。则当此之时。圣凡无间。苟其有体察之顷。则乃真心已冷。私意横出之时。不可谓当恻隐时。须看这当字十分紧急。至若观物度身。容或有可议者。然苟以是为一槩法门。则支离纷挐。转益躁扰。安得有通透深纯之效乎。比并较量。毕竟长得私意。将身为物缚而心为物窒矣。
太极之有方横竖倒。钟说甚新。何敢自信。但其意则亦何尝谓太极之有此许多般样。而各占部伍。交峙并据于宇宙之间耶。只就浑圆中分析教丁宁耳。虽方横竖倒。其分甚殊。而合而观之则浑然是大圆而已。方其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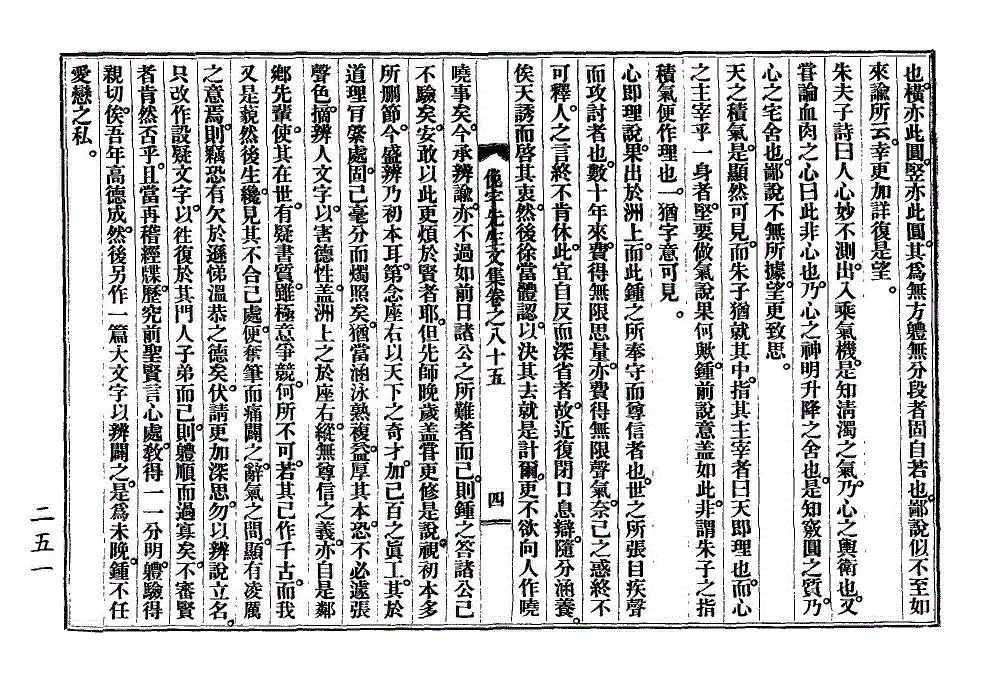 也。横亦此圆。竖亦此圆。其为无方体无分段者固自若也。鄙说似不至如来谕所云。幸更加详复是望。
也。横亦此圆。竖亦此圆。其为无方体无分段者固自若也。鄙说似不至如来谕所云。幸更加详复是望。朱夫子诗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是知清浊之气。乃心之舆卫也。又尝论血肉之心曰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也。是知窍圆之质。乃心之宅舍也。鄙说不无所据。望更致思。
天之积气。是显然可见。而朱子犹就其中。指其主宰者曰天即理也。而心之主宰乎一身者。坚要做气说果何欤。钟前说意盖如此。非谓朱子之指积气便作理也。一犹字意可见。
心即理说。果出于洲上。而此钟之所奉守而尊信者也。世之所张目疾声而攻讨者也。数十年来。费得无限思量。亦费得无限声气。奈已之惑终不可释。人之言终不肯休。此宜自反而深省者。故近复闭口息辩。随分涵养。俟天诱而启其衷。然后徐当体认。以决其去就是计尔。更不欲向人作哓哓事矣。今承辨谕。亦不过如前日诸公之所难者而已。则钟之答诸公已不验矣。安敢以此更烦于贤者耶。但先师晚岁盖尝更修是说。视初本多所删节。今盛辨乃初本耳。第念座右以天下之奇才。加已百之真工。其于道理肯綮处。固已毫分而烛照矣。犹当涵泳熟复。益厚其本。恐不必遽张声色。摘辨人文字。以害德性。盖洲上之于座右。纵无尊信之义。亦自是邻乡先辈。使其在世。有疑书质。虽极意争竞。何所不可。若其已作千古。而我又是藐然后生。才见其不合已处。便奋笔而痛辟之。辞气之间。显有凌厉之意焉。则窃恐有欠于逊悌温恭之德矣。伏请更加深思。勿以辨说立名。只改作设疑文字。以往复于其门人子弟而已。则体顺而过寡矣。不审贤者肯然否乎。且当再稽经牒。历究前圣贤言心处。教得一一分明。体验得亲切。俟吾年高德成。然后另作一篇大文字以辨辟之。是为未晚。钟不任爱恋之私。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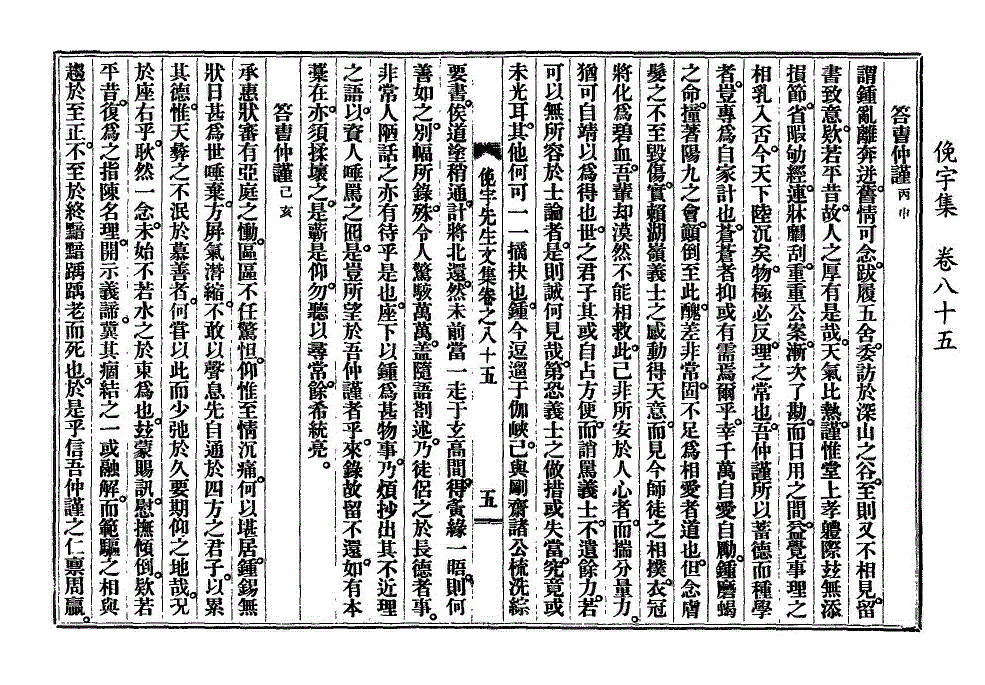 答曹仲谨(丙申)
答曹仲谨(丙申)谓钟乱离奔迸。旧情可念。跋履五舍。委访于深山之谷。至则又不相见。留书致意。款若平昔。故人之厚有是哉。天气比热。谨惟堂上孝体际玆无添损节。省暇劬经。连床劘刮。重重公案。渐次了勘。而日用之间。益觉事理之相乳入否。今天下陆沉矣。物极必反。理之常也。吾仲谨所以蓄德而种学者。岂专为自家计也。苍苍者抑或有需焉尔乎。幸千万自爱自励。钟磨蝎之命。撞著阳九之会。颠倒至此。丑差非常。固不足为相爱者道也。但念肤发之不至毁伤。实赖湖岭义士之感动得天意。而见今师徒之相扑。衣冠将化为碧血。吾辈却漠然不能相救。此已非所安于人心者。而揣分量力。犹可自靖以为得也。世之君子其或自占方便。而诮骂义士。不遗馀力。若可以无所容于士论者。是则诚何见哉。第恐义士之做措或失当。究竟或未光耳。其他何可一一摘抉也。钟今逗遛于伽峡。已与刚斋诸公梳洗综要书。俟道涂稍通。计将北还。然未前当一走于玄高间。得夤缘一晤。则何善如之。别幅所录。殊令人惊骇万万。盖随语劄述。乃徒侣之于长德者事。非常人陋话之亦有待乎是也。座下以钟为甚物事。乃烦抄出其不近理之语。以资人唾骂之囮。是岂所望于吾仲谨者乎。来录故留不还。如有本藁在。亦须揉坏之。是蕲是仰。勿听以寻常。馀希统亮。
答曹仲谨(己亥)
承惠状审有亚庭之恸。区区不任惊怛。仰惟至情沉痛。何以堪居。钟锡无状日甚为世唾弃。方屏气潜缩。不敢以声息先自通于四方之君子。以累其德。惟天彝之不泯于慕善者。何尝以此而少弛于久要期仰之地哉。况于座右乎。耿然一念。未始不若水之于东为也。玆蒙赐讯。慰抚倾倒。款若平昔。复为之指陈名理。开示义谛。冀其痼结之一或融解。而范驱之相与趋于至正。不至于终黯黯踽踽老而死也。于是乎信吾仲谨之仁禀周赢。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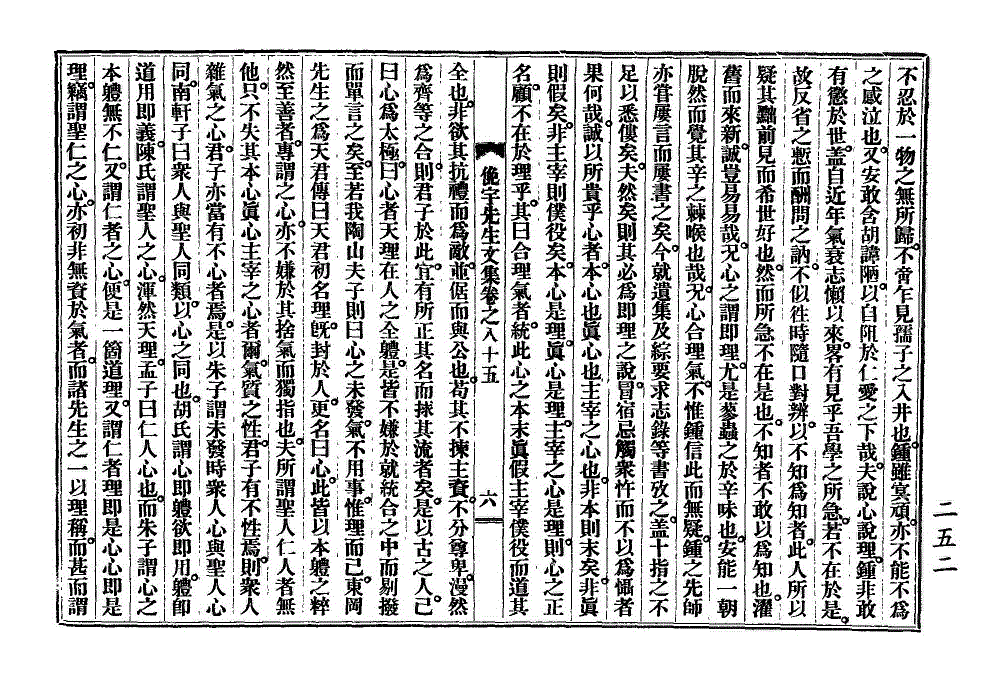 不忍于一物之无所归。不啻乍见孺子之入井也。钟虽冥顽。亦不能不为之感泣也。又安敢含胡讳陋。以自阻于仁爱之下哉。夫说心说理。钟非敢有惩于世。盖自近年气衰志懒以来。略有见乎吾学之所急。若不在于是。故反省之惭而酬问之讷。不似往时随口对辨。以不知为知者。此人所以疑其黜前见而希世好也。然而所急不在是也。不知者不敢以为知也。濯旧而来新。诚岂易易哉。况心之谓即理。尤是蓼虫之于辛味也。安能一朝脱然而觉其辛之棘喉也哉。况心合理气。不惟钟信此而无疑。钟之先师亦尝屡言而屡书之矣。今就遗集及综要求志录等书考之。盖十指之不足以悉偻矣。夫然矣则其必为即理之说。冒宿忌触众忤而不以为慑者果何哉。诚以所贵乎心者。本心也真心也,主宰之心也。非本则末矣。非真则假矣。非主宰则仆役矣。本心是理。真心是理。主宰之心是理。则心之正名。顾不在于理乎。其曰合理气者。统此心之本末真假主宰仆役而道其全也。非欲其抗礼而为敌。并倨而与公也。苟其不拣主资。不分尊卑。漫然为齐等之合。则君子于此。宜有所正其名而救其流者矣。是以古之人。已曰心为太极。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是皆不嫌于就统合之中而剔拨而单言之矣。至若我陶山夫子则曰心之未发。气不用事。惟理而已。东冈先生之为天君传曰天君初名理。既封于人。更名曰心。此皆以本体之粹然至善者。专谓之心。亦不嫌于其舍气而独指也。夫所谓圣人仁人者无他。只不失其本心真心主宰之心者尔。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焉。则众人杂气之心。君子亦当有不心者焉。是以朱子谓未发时众人心与圣人心同。南轩子曰众人与圣人同类。以心之同也。胡氏谓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陈氏谓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孟子曰仁人心也。而朱子谓心之本体无不仁。又谓仁者之心。便是一个道理。又谓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窃谓圣仁之心。亦初非无资于气者。而诸先生之一以理称。而甚而谓
不忍于一物之无所归。不啻乍见孺子之入井也。钟虽冥顽。亦不能不为之感泣也。又安敢含胡讳陋。以自阻于仁爱之下哉。夫说心说理。钟非敢有惩于世。盖自近年气衰志懒以来。略有见乎吾学之所急。若不在于是。故反省之惭而酬问之讷。不似往时随口对辨。以不知为知者。此人所以疑其黜前见而希世好也。然而所急不在是也。不知者不敢以为知也。濯旧而来新。诚岂易易哉。况心之谓即理。尤是蓼虫之于辛味也。安能一朝脱然而觉其辛之棘喉也哉。况心合理气。不惟钟信此而无疑。钟之先师亦尝屡言而屡书之矣。今就遗集及综要求志录等书考之。盖十指之不足以悉偻矣。夫然矣则其必为即理之说。冒宿忌触众忤而不以为慑者果何哉。诚以所贵乎心者。本心也真心也,主宰之心也。非本则末矣。非真则假矣。非主宰则仆役矣。本心是理。真心是理。主宰之心是理。则心之正名。顾不在于理乎。其曰合理气者。统此心之本末真假主宰仆役而道其全也。非欲其抗礼而为敌。并倨而与公也。苟其不拣主资。不分尊卑。漫然为齐等之合。则君子于此。宜有所正其名而救其流者矣。是以古之人。已曰心为太极。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是皆不嫌于就统合之中而剔拨而单言之矣。至若我陶山夫子则曰心之未发。气不用事。惟理而已。东冈先生之为天君传曰天君初名理。既封于人。更名曰心。此皆以本体之粹然至善者。专谓之心。亦不嫌于其舍气而独指也。夫所谓圣人仁人者无他。只不失其本心真心主宰之心者尔。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焉。则众人杂气之心。君子亦当有不心者焉。是以朱子谓未发时众人心与圣人心同。南轩子曰众人与圣人同类。以心之同也。胡氏谓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陈氏谓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孟子曰仁人心也。而朱子谓心之本体无不仁。又谓仁者之心。便是一个道理。又谓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窃谓圣仁之心。亦初非无资于气者。而诸先生之一以理称。而甚而谓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3H 页
 理即心心即理。不虞其或遗乎气者。其意固在于本心真心主宰之心。而不必每每及于其末其假其仆役者之不足深恃者耳。若曰圣仁之心。是心之一偏。而非心之本真也。是圣仁为弃本而丧真者。而众人心之理气迭胜。真妄相杂者。方得为心之正面矣。其然乎不然乎。心与性。有分言时。有合言时。盖泛言心则合气而直指本心则理而已。故其分言于性者。从合气处看。合言于性者。从直指处看。今一例谓圣人界之。故百事序而精。释氏乱之。故百事紊而杂云尔。则程子曰心即性也。曰心也性也一理也。朱子曰心与性只一般。曰心只是一个性。曰心无体。以性为体。曰心性一物。此等岂皆全昧于真妄理气之别。而不觉其自陷于释氏乱之之科耶。来谕且引朱子所谓气质所赋。虽有不同。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无省察矫揉之功。而曰此奚独论性。而可说心尤有力焉。钟以为诚然诚然。夫性或杂气。而指其本善曰性即理也。心之合气而亦指其本善曰心即理也。不言即理则人不知此心之本善。而将以真妄之相杂者为本心矣。不言合气则人不肯下省察矫揉之功。而将以此心之发。为无非至理。率意而妄行矣。若是乎盛见之不啻左右契于鄙怀也。来谕且谓唐虞君臣之相亲如家人。相规如朋友。秦之尊君抑臣。天下大乱。以證主理之非。然则唐虞君臣果无尊卑之定分。而尧或北面于舜。舜或肩随于尧耶。虽相亲如家人而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分截然而不可干矣。相规如朋友则人之为君臣。人则同也。箴戒论思。可以相正。理气之为君臣。理纯善而气或恶。理至公而气或私。理有知而气无知。宁可以气而规理。以理而从气。所规若朋友之相敌者乎。人之为君。有善有不善。故尧舜之君而吁咈于共鲧。都俞于禹皋陶则天下治。吕政之君焉。而纵其都俞于斯高。天下其不乱乎。理之为君也。无时而不尧舜也。苟其自作主宰。命气而不命于气焉。则天下其有治而无乱矣。惟其自失主宰。认斯高为禹皋陶。假
理即心心即理。不虞其或遗乎气者。其意固在于本心真心主宰之心。而不必每每及于其末其假其仆役者之不足深恃者耳。若曰圣仁之心。是心之一偏。而非心之本真也。是圣仁为弃本而丧真者。而众人心之理气迭胜。真妄相杂者。方得为心之正面矣。其然乎不然乎。心与性。有分言时。有合言时。盖泛言心则合气而直指本心则理而已。故其分言于性者。从合气处看。合言于性者。从直指处看。今一例谓圣人界之。故百事序而精。释氏乱之。故百事紊而杂云尔。则程子曰心即性也。曰心也性也一理也。朱子曰心与性只一般。曰心只是一个性。曰心无体。以性为体。曰心性一物。此等岂皆全昧于真妄理气之别。而不觉其自陷于释氏乱之之科耶。来谕且引朱子所谓气质所赋。虽有不同。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无省察矫揉之功。而曰此奚独论性。而可说心尤有力焉。钟以为诚然诚然。夫性或杂气。而指其本善曰性即理也。心之合气而亦指其本善曰心即理也。不言即理则人不知此心之本善。而将以真妄之相杂者为本心矣。不言合气则人不肯下省察矫揉之功。而将以此心之发。为无非至理。率意而妄行矣。若是乎盛见之不啻左右契于鄙怀也。来谕且谓唐虞君臣之相亲如家人。相规如朋友。秦之尊君抑臣。天下大乱。以證主理之非。然则唐虞君臣果无尊卑之定分。而尧或北面于舜。舜或肩随于尧耶。虽相亲如家人而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分截然而不可干矣。相规如朋友则人之为君臣。人则同也。箴戒论思。可以相正。理气之为君臣。理纯善而气或恶。理至公而气或私。理有知而气无知。宁可以气而规理。以理而从气。所规若朋友之相敌者乎。人之为君。有善有不善。故尧舜之君而吁咈于共鲧。都俞于禹皋陶则天下治。吕政之君焉。而纵其都俞于斯高。天下其不乱乎。理之为君也。无时而不尧舜也。苟其自作主宰。命气而不命于气焉。则天下其有治而无乱矣。惟其自失主宰。认斯高为禹皋陶。假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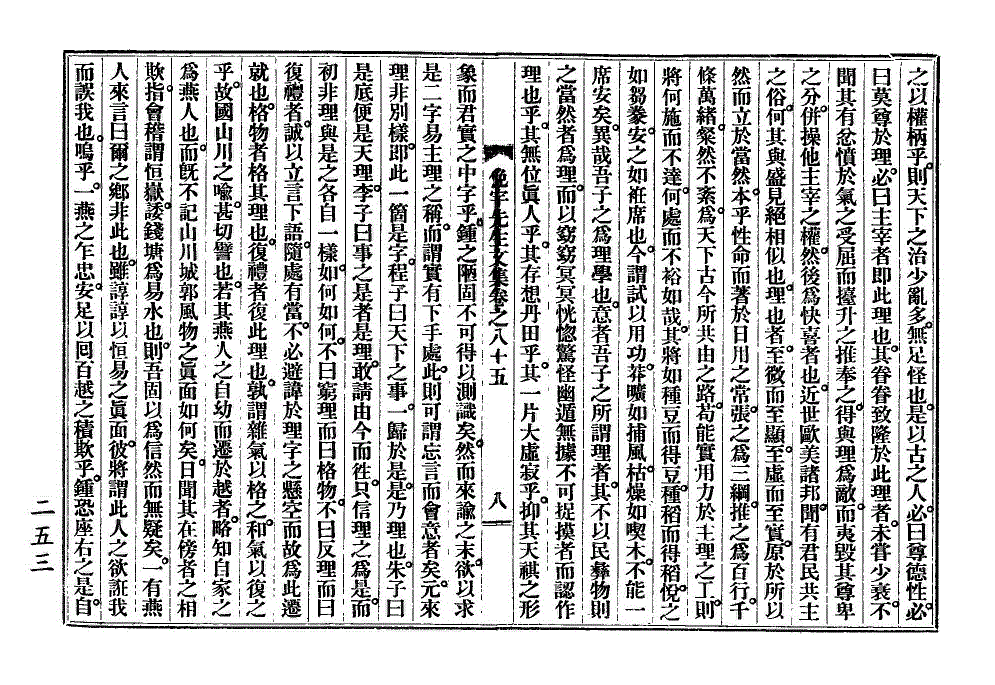 之以权柄乎。则天下之治少乱多。无足怪也。是以古之人。必曰尊德性。必曰莫尊于理。必曰主宰者即此理也。其眷眷致隆于此理者。未尝少衰。不闻其有忿愤于气之受屈而抬升之推奉之。得与理为敌。而夷毁其尊卑之分。并操他主宰之权。然后为快喜者也。近世欧美诸邦。闻有君民共主之俗。何其与盛见绝相似也。理也者。至微而至显。至虚而至实。原于所以然而立于当然。本乎性命而著于日用之常。张之为三纲。推之为百行。千条万绪。粲然不紊。为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苟能实用力于主理之工。则将何施而不达。何处而不裕如哉。其将如种豆而得豆。种稻而得稻。悦之如刍豢。安之如衽席也。今谓试以用功。莽旷如捕风。枯燥如吃木。不能一席安矣。异哉吾子之为理学也。意者吾子之所谓理者。其不以民彝物则之当然者为理。而以窈窈冥冥恍惚惊怪幽遁无据不可捉摸者而认作理也乎。其无位真人乎。其存想丹田乎。其一片大虚寂乎。抑其天祺之形象而君实之中字乎。钟之陋固不可得以测识矣。然而来谕之末。欲以求是二字易主理之称。而谓实有下手处。此则可谓忘言而会意者矣。元来理非别样。即此一个是字。程子曰天下之事。一归于是。是乃理也。朱子曰是底便是天理。李子曰事之是者是理。敢请由今而往。只信理之为是。而初非理与是之各自一样。如何如何。不曰穷理而曰格物。不曰反理而曰复礼者。诚以立言下语。随处有当。不必避讳于理字之悬空而故为此迁就也。格物者格其理也。复礼者复此理也。孰谓杂气以格之。和气以复之乎。故国山川之喻。甚切譬也。若其燕人之自幼而迁于越者。略知自家之为燕人也。而既不记山川城郭风物之真面如何矣。日闻其在傍者之相欺。指会稽谓恒岳。诿钱塘为易水也。则吾固以为信然而无疑矣。一有燕人来言曰尔之乡非此也。虽谆谆以恒易之真面。彼将谓此人之欲诳我而误我也。呜乎。一燕之乍忠。安足以回百越之积欺乎。钟恐座右之是。自
之以权柄乎。则天下之治少乱多。无足怪也。是以古之人。必曰尊德性。必曰莫尊于理。必曰主宰者即此理也。其眷眷致隆于此理者。未尝少衰。不闻其有忿愤于气之受屈而抬升之推奉之。得与理为敌。而夷毁其尊卑之分。并操他主宰之权。然后为快喜者也。近世欧美诸邦。闻有君民共主之俗。何其与盛见绝相似也。理也者。至微而至显。至虚而至实。原于所以然而立于当然。本乎性命而著于日用之常。张之为三纲。推之为百行。千条万绪。粲然不紊。为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苟能实用力于主理之工。则将何施而不达。何处而不裕如哉。其将如种豆而得豆。种稻而得稻。悦之如刍豢。安之如衽席也。今谓试以用功。莽旷如捕风。枯燥如吃木。不能一席安矣。异哉吾子之为理学也。意者吾子之所谓理者。其不以民彝物则之当然者为理。而以窈窈冥冥恍惚惊怪幽遁无据不可捉摸者而认作理也乎。其无位真人乎。其存想丹田乎。其一片大虚寂乎。抑其天祺之形象而君实之中字乎。钟之陋固不可得以测识矣。然而来谕之末。欲以求是二字易主理之称。而谓实有下手处。此则可谓忘言而会意者矣。元来理非别样。即此一个是字。程子曰天下之事。一归于是。是乃理也。朱子曰是底便是天理。李子曰事之是者是理。敢请由今而往。只信理之为是。而初非理与是之各自一样。如何如何。不曰穷理而曰格物。不曰反理而曰复礼者。诚以立言下语。随处有当。不必避讳于理字之悬空而故为此迁就也。格物者格其理也。复礼者复此理也。孰谓杂气以格之。和气以复之乎。故国山川之喻。甚切譬也。若其燕人之自幼而迁于越者。略知自家之为燕人也。而既不记山川城郭风物之真面如何矣。日闻其在傍者之相欺。指会稽谓恒岳。诿钱塘为易水也。则吾固以为信然而无疑矣。一有燕人来言曰尔之乡非此也。虽谆谆以恒易之真面。彼将谓此人之欲诳我而误我也。呜乎。一燕之乍忠。安足以回百越之积欺乎。钟恐座右之是。自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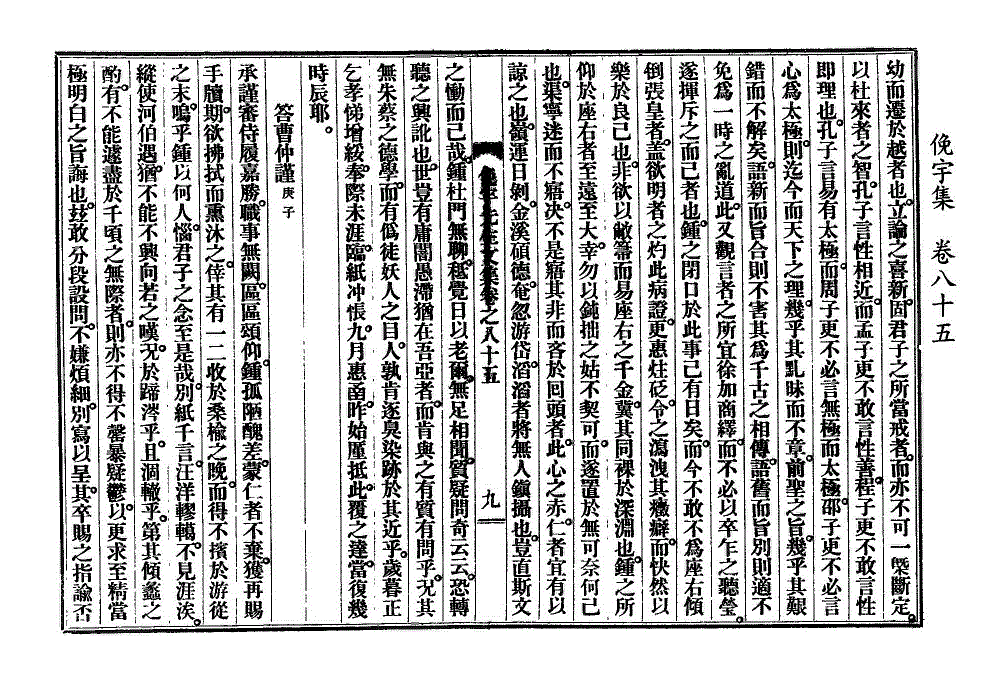 幼而迁于越者也。立论之喜新。固君子之所当戒者。而亦不可一槩断定。以杜来者之智。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更不敢言性善。程子更不敢言性即理也。孔子言易有太极。而周子更不必言无极而太极。邵子更不必言心为太极。则迄今而天下之理。几乎其䵝昧而不章。前圣之旨。几乎其艰错而不解矣。语新而旨合则不害其为千古之相传。语旧而旨别则适不免为一时之乱道。此又观言者之所宜徐加商绎。而不必以卒乍之听莹。遂挥斥之而已者也。钟之闭口于此事已有日矣。而今不敢不为座右倾倒张皇者。盖欲明者之灼此病證。更惠炷砭。令之泻泄其症癖。而快然以乐于良已也。非欲以敝帚而易座右之千金。冀其同裸于深渊也。钟之所仰于座右者至远至大。幸勿以钝拙之姑不契可。而遂置于无可奈何已也。渠宁迷而不寤。决不是寤其非而吝于回头者。此心之赤。仁者宜有以谅之也。岭运日剥。金溪硕德。奄忽游岱。滔滔者将无人镇摄也。岂直斯文之恸而已哉。钟杜门无聊。秪觉日以老尔。无足相闻。质疑问奇云云。恐转听之兴讹也。世岂有庸闇愚滞犹在吾亚者。而肯与之有质有问乎。况其无朱蔡之德学。而有伪徒妖人之目。人孰肯逐臭染迹于其近乎。岁暮正乞孝悌增绥。奉际未涯。临纸冲怅。九月惠函。昨始廑抵。此覆之达。当复几时辰耶。
幼而迁于越者也。立论之喜新。固君子之所当戒者。而亦不可一槩断定。以杜来者之智。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更不敢言性善。程子更不敢言性即理也。孔子言易有太极。而周子更不必言无极而太极。邵子更不必言心为太极。则迄今而天下之理。几乎其䵝昧而不章。前圣之旨。几乎其艰错而不解矣。语新而旨合则不害其为千古之相传。语旧而旨别则适不免为一时之乱道。此又观言者之所宜徐加商绎。而不必以卒乍之听莹。遂挥斥之而已者也。钟之闭口于此事已有日矣。而今不敢不为座右倾倒张皇者。盖欲明者之灼此病證。更惠炷砭。令之泻泄其症癖。而快然以乐于良已也。非欲以敝帚而易座右之千金。冀其同裸于深渊也。钟之所仰于座右者至远至大。幸勿以钝拙之姑不契可。而遂置于无可奈何已也。渠宁迷而不寤。决不是寤其非而吝于回头者。此心之赤。仁者宜有以谅之也。岭运日剥。金溪硕德。奄忽游岱。滔滔者将无人镇摄也。岂直斯文之恸而已哉。钟杜门无聊。秪觉日以老尔。无足相闻。质疑问奇云云。恐转听之兴讹也。世岂有庸闇愚滞犹在吾亚者。而肯与之有质有问乎。况其无朱蔡之德学。而有伪徒妖人之目。人孰肯逐臭染迹于其近乎。岁暮正乞孝悌增绥。奉际未涯。临纸冲怅。九月惠函。昨始廑抵。此覆之达。当复几时辰耶。答曹仲谨(庚子)
承谨审侍履嘉胜。职事无阙。区区颂仰。钟孤陋丑差。蒙仁者不弃。获再赐手牍。期欲拂拭而熏沐之。倖其有一二收于桑榆之晚。而得不摈于游从之末。呜乎钟以何人。恼君子之念至是哉。别纸千言。汪洋轇轕。不见涯涘。纵使河伯遇。犹不能不兴向若之叹。况于蹄涔乎。且涸辙乎。第其倾蠡之酌。有不能遽尽于千顷之无际者。则亦不得不罄暴疑郁。以更求至精当极明白之旨诲也。玆敢分段设问。不嫌烦细。别写以呈。其卒赐之指谕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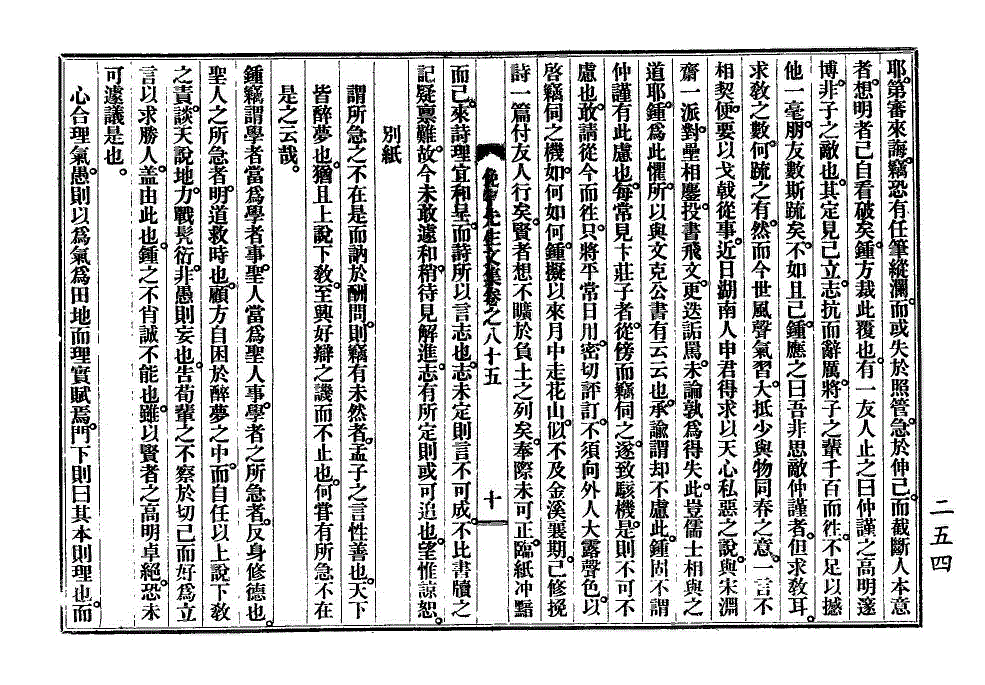 耶。第审来诲。窃恐有任笔纵澜。而或失于照管。急于伸己。而截断人本意者。想明者已自看破矣。钟方裁此覆也。有一友人止之曰仲谨之高明邃博。非子之敌也。其定见已立。志抗而辞厉。将子之辈千百而往。不足以撼他一毫。朋友数斯疏矣。不如且已。钟应之曰吾非思敌仲谨者。但求教耳。求教之数。何疏之有。然而今世风声气习。大抵少与物同春之意。一言不相契。便要以戈戟从事。近日湖南人申君得求以天心私恶之说。与宋渊斋一派。对垒相鏖。投书飞文。更迭诟骂。未论孰为得失。此岂儒士相与之道耶。钟为此惧。所以与文克公书有云云也。承谕谓却不虑此。钟固不谓仲谨有此虑也。每常见卞庄子者。从傍而窃伺之。遂致骇机。是则不可不虑也。敢请从今而往。只将平常日用。密切评订。不须向外人大露声色。以启窃伺之机。如何如何。钟拟以来月中走花山。似不及金溪襄期。已修挽诗一篇付友人行矣。贤者想不旷于负土之列矣。奉际未可正。临纸冲黯而已。来诗理宜和呈。而诗所以言志也。志未定则言不可成。不比书牍之记疑禀难。故今未敢遽和。稍待见解进。志有所定则或可追也。望惟谅恕。
耶。第审来诲。窃恐有任笔纵澜。而或失于照管。急于伸己。而截断人本意者。想明者已自看破矣。钟方裁此覆也。有一友人止之曰仲谨之高明邃博。非子之敌也。其定见已立。志抗而辞厉。将子之辈千百而往。不足以撼他一毫。朋友数斯疏矣。不如且已。钟应之曰吾非思敌仲谨者。但求教耳。求教之数。何疏之有。然而今世风声气习。大抵少与物同春之意。一言不相契。便要以戈戟从事。近日湖南人申君得求以天心私恶之说。与宋渊斋一派。对垒相鏖。投书飞文。更迭诟骂。未论孰为得失。此岂儒士相与之道耶。钟为此惧。所以与文克公书有云云也。承谕谓却不虑此。钟固不谓仲谨有此虑也。每常见卞庄子者。从傍而窃伺之。遂致骇机。是则不可不虑也。敢请从今而往。只将平常日用。密切评订。不须向外人大露声色。以启窃伺之机。如何如何。钟拟以来月中走花山。似不及金溪襄期。已修挽诗一篇付友人行矣。贤者想不旷于负土之列矣。奉际未可正。临纸冲黯而已。来诗理宜和呈。而诗所以言志也。志未定则言不可成。不比书牍之记疑禀难。故今未敢遽和。稍待见解进。志有所定则或可追也。望惟谅恕。别纸
谓所急之不在是而讷于酬问。则窃有未然者。孟子之言性善也。天下皆醉梦也。犹且上说下教。至兴好辩之讥而不止也。何尝有所急不在是之云哉。
钟窃谓学者当为学者事。圣人当为圣人事。学者之所急者。反身修德也。圣人之所急者。明道救时也。顾方自困于醉梦之中。而自任以上说下教之责。谈天说地。力战髡衍。非愚则妄也。告荀辈之不察于切己而好为立言以求胜人。盖由此也。钟之不肖诚不能也。虽以贤者之高明卓绝。恐未可遽议是也。
心合理气。愚则以为气为田地而理实赋焉。门下则曰其本则理也。而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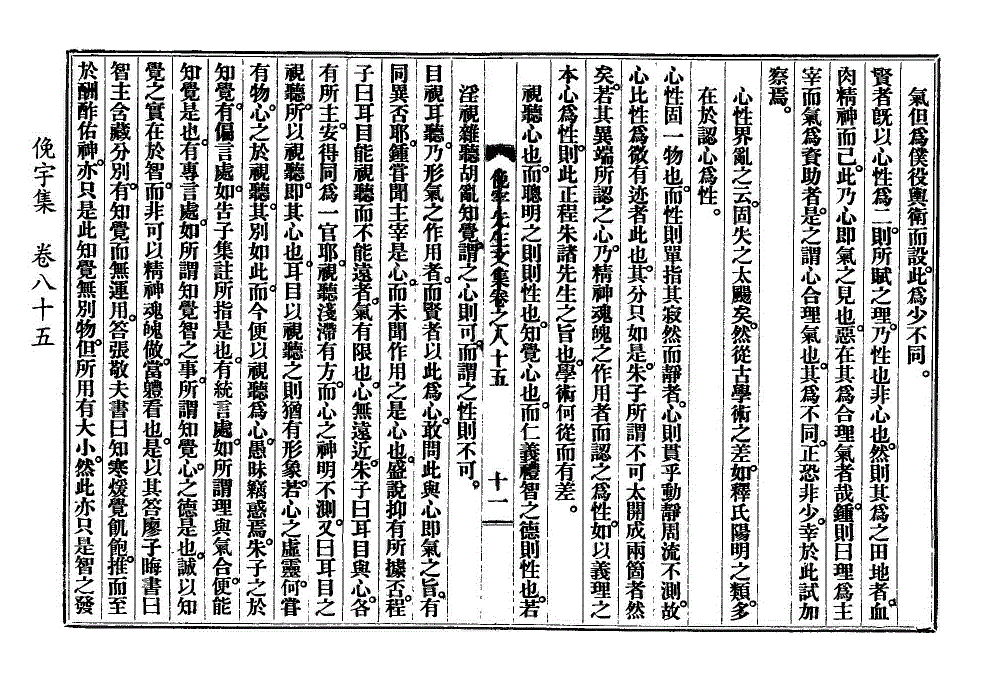 气但为仆役舆卫而设。此为少不同。
气但为仆役舆卫而设。此为少不同。贤者既以心性为二。则所赋之理。乃性也非心也然则其为之田地者。血肉精神而已。此乃心即气之见也。恶在其为合理气者哉。钟则曰理为主宰而气为资助者。是之谓心合理气也。其为不同。正恐非少。幸于此试加察焉。
心性界乱之云。固失之太飏矣。然从古学术之差。如释氏阳明之类。多在于认心为性。
心性固一物也。而性则单指其寂然而静者。心则贯乎动静周流不测。故心比性为微有迹者此也。其分只如是。朱子所谓不可太开成两个者然矣。若其异端所认之心。乃精神魂魄之作用者而认之为性。如以义理之本心为性。则此正程朱诸先生之旨也。学术何从而有差。
视听心也。而聪明之则则性也。知觉心也。而仁义礼智之德则性也。若淫视杂听胡乱知觉。谓之心则可。而谓之性则不可。
目视耳听。乃形气之作用者。而贤者以此为心。敢问此与心即气之旨。有同异否耶。钟尝闻主宰是心。而未闻作用之是心也。盛说抑有所据否。程子曰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也。心无远近。朱子曰耳目与心。各有所主。安得同为一官耶。视听浅滞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测。又曰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即其心也。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心之于视听。其别如此。而今便以视听为心。愚昧窃惑焉。朱子之于知觉。有偏言处。如告子集注所指是也。有统言处。如所谓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是也。有专言处。如所谓知觉智之事。所谓知觉。心之德是也。诚以知觉之实在于智。而非可以精神魂魄做。当体看也。是以其答廖子晦书曰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答张敬夫书曰知寒煖觉饥饱。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但所用有大小。然此亦只是智之发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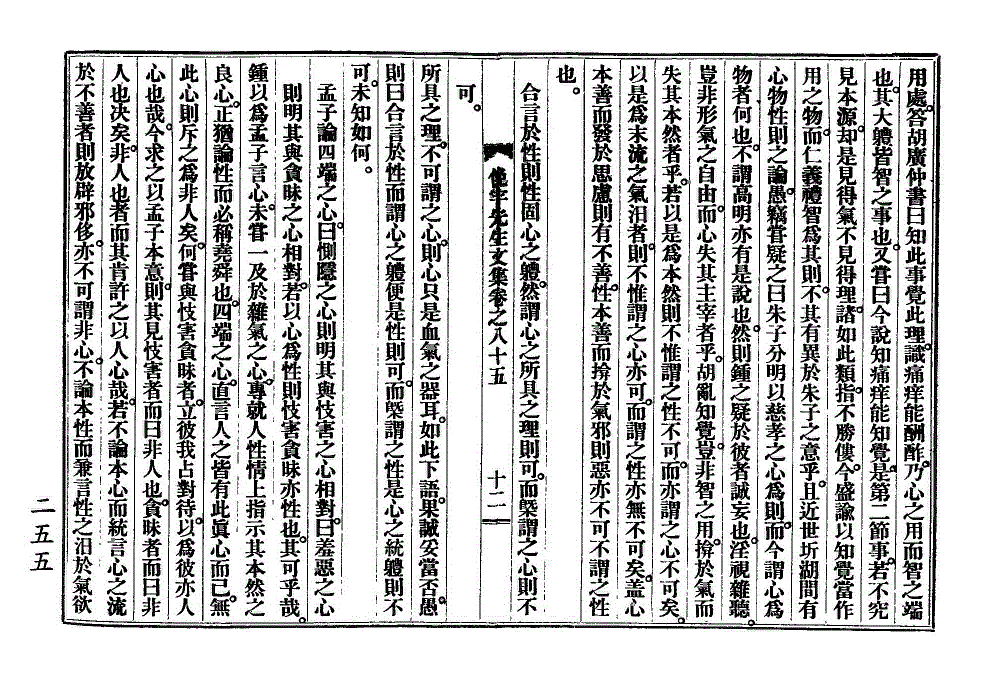 用处。答胡广仲书曰知此事觉此理。识痛痒能酬酢。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其大体皆智之事也。又尝曰今说知痛痒能知觉。是第二节事。若不究见本源。却是见得气不见得理。诸如此类。指不胜偻。今盛谕以知觉当作用之物。而仁义礼智为其则。不其有异于朱子之意乎。且近世圻湖间有心物性则之论。愚窃尝疑之曰朱子分明以慈孝之心为则。而今谓心为物者何也。不谓高明亦有是说也。然则钟之疑于彼者诚妄也。淫视杂听。岂非形气之自由。而心失其主宰者乎。胡乱知觉。岂非智之用。掩于气而失其本然者乎。若以是为本然则不惟谓之性不可。而亦谓之心不可矣。以是为末流之气汩者。则不惟谓之心亦可。而谓之性亦无不可矣。盖心本善而发于思虑则有不善。性本善而掩于气邪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用处。答胡广仲书曰知此事觉此理。识痛痒能酬酢。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其大体皆智之事也。又尝曰今说知痛痒能知觉。是第二节事。若不究见本源。却是见得气不见得理。诸如此类。指不胜偻。今盛谕以知觉当作用之物。而仁义礼智为其则。不其有异于朱子之意乎。且近世圻湖间有心物性则之论。愚窃尝疑之曰朱子分明以慈孝之心为则。而今谓心为物者何也。不谓高明亦有是说也。然则钟之疑于彼者诚妄也。淫视杂听。岂非形气之自由。而心失其主宰者乎。胡乱知觉。岂非智之用。掩于气而失其本然者乎。若以是为本然则不惟谓之性不可。而亦谓之心不可矣。以是为末流之气汩者。则不惟谓之心亦可。而谓之性亦无不可矣。盖心本善而发于思虑则有不善。性本善而掩于气邪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合言于性则性固心之体。然谓心之所具之理则可。而槩谓之心则不可。
所具之理。不可谓之心。则心只是血气之器耳。如此下语。果诚妥当否。愚则曰合言于性而谓心之体便是性则可。而槩谓之性是心之统体则不可。未知如何。
孟子论四端之心。曰恻隐之心则明其与忮害之心相对。曰羞恶之心则明其与贪昧之心相对。若以心为性则忮害贪昧亦性也。其可乎哉。
钟以为孟子言心。未尝一及于杂气之心。专就人性情上指示其本然之良心。正犹论性而必称尧舜也。四端之心。直言人之皆有此真心而已。无此心则斥之为非人矣。何尝与忮害贪昧者。立彼我占对待。以为彼亦人心也哉。今求之以孟子本意。则其见忮害者而曰非人也。贪昧者而曰非人也决矣。非人也者而其肯许之以人心哉。若不论本心而统言心之流于不善者则放辟邪侈。亦不可谓非心。不论本性而兼言性之汩于气欲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6H 页
 者则忮害贪昧亦不得不谓之性。周子之以刚柔善恶均谓之性。以此也。
者则忮害贪昧亦不得不谓之性。周子之以刚柔善恶均谓之性。以此也。紫阳夫子一生费尽心力。苦苦斥佛斥禅。未尝不认此为第一义。玉山讲义中尤发明之。
朱先生之所苦心于斥禅佛者。正在于彼之认精神作用为心尔。如其以义理主宰之心。心之德智之事之知觉而合言于性理乎则岂其亦在所斥之科乎。讲义所谓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者。正谓以冲漠之性而看作思虑较计之物。非谓知觉心意之本体都不可做性看也。是以讲义在甲寅。而同年盖卿录曰横渠说大率未莹。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戊午僩录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恐不能无病。恰似性外别有知觉。盖横渠则言知觉之用。而朱子又恐一向如此。则或疑知觉本体。反在性外。故为此说以救之也。此与讲义所云虽若相戾。而其实相足也。今一切谓之苦苦斥彼认此为第一义可乎。其答郑子上曰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然近世一种之学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故其发亦不合理。却与释氏同病。此则分合俱勘说得无渗漏者也。请就此。贤者则以上一截为戒。钟则以下一截为惧。交相修饬。庶几不堕于释氏之病。而无负朱夫子苦心否。如何如何。
圣人界之之说则岂敢以圣人为舍性而求心。亡心而养性。但以为异于释氏所谓耳。
圣人之于心性。本体则合之。发用则界之。释氏之于心性。认发用为本体。其合也适所以界之也。认理为此心之障。其分也适所以乱之也。初非圣人之一于分界。而释氏之一于合乱也。若谓圣人之分而无合则其不至于舍性而求心。亡心而养性乎。贤者前书都无一言及于心性之合。而只说界之为正而合之为乱。藉令本意有在。得非下语之疏漏乎。钝滞如钟宜其未遽喻也。玆承更示。稍以释一半之惑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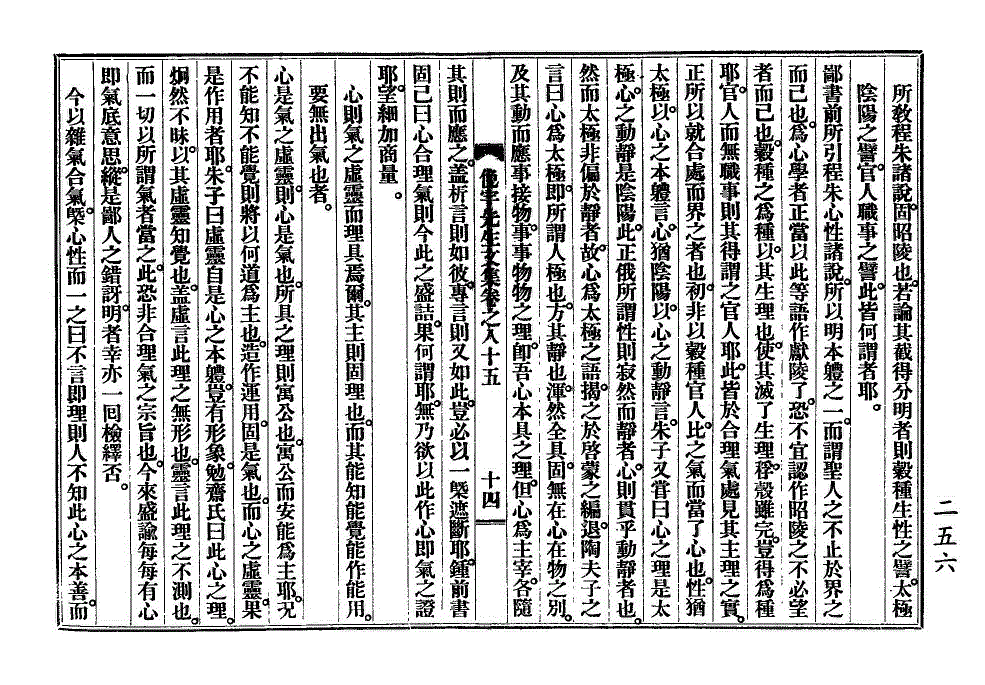 所教程朱诸说。固昭陵也。若论其截得分明者则谷种生性之譬。太极阴阳之譬。官人职事之譬。此皆何谓者耶。
所教程朱诸说。固昭陵也。若论其截得分明者则谷种生性之譬。太极阴阳之譬。官人职事之譬。此皆何谓者耶。鄙书前所引程朱心性诸说。所以明本体之一。而谓圣人之不止于界之而已也。为心学者正当以此等语作献陵了。恐不宜认作昭陵之不必望者而已也。谷种之为种。以其生理也。使其灭了生理。稃壳虽完。岂得为种耶。官人而无职事则其得谓之官人耶。此皆于合理气处见其主理之实。正所以就合处而界之者也。初非以谷种官人。比之气而当了心也。性犹太极。以心之本体言。心犹阴阳。以心之动静言。朱子又尝曰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此正俄所谓性则寂然而静者。心则贯乎动静者也。然而太极非偏于静者。故心为太极之语。揭之于启蒙之编。退陶夫子之言曰心为太极。即所谓人极也。方其静也。浑然全具。固无在心在物之别。及其动而应事接物。事事物物之理。即吾心本具之理。但心为主宰。各随其则而应之。盖析言则如彼。专言则又如此。岂必以一槩遮断耶。钟前书固已曰心合理气则今此之盛诘。果何谓耶。无乃欲以此作心即气之證耶。望细加商量。
心则气之虚灵而理具焉尔。其主则固理也。而其能知能觉能作能用。要无出气也者。
心是气之虚灵。则心是气也。所具之理则寓公也。寓公而安能为主耶。况不能知不能觉则将以何道为主也。造作运用。固是气也。而心之虚灵。果是作用者耶。朱子曰虚灵自是心之本体。岂有形象。勉斋氏曰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以其虚灵知觉也。盖虚言此理之无形也。灵言此理之不测也。而一切以所谓气者当之。此恐非合理气之宗旨也。今来盛谕每每有心即气底意思。纵是鄙人之错讶。明者幸亦一回检绎否。
今以杂气合气。槩心性而一之曰不言即理则人不知此心之本善。而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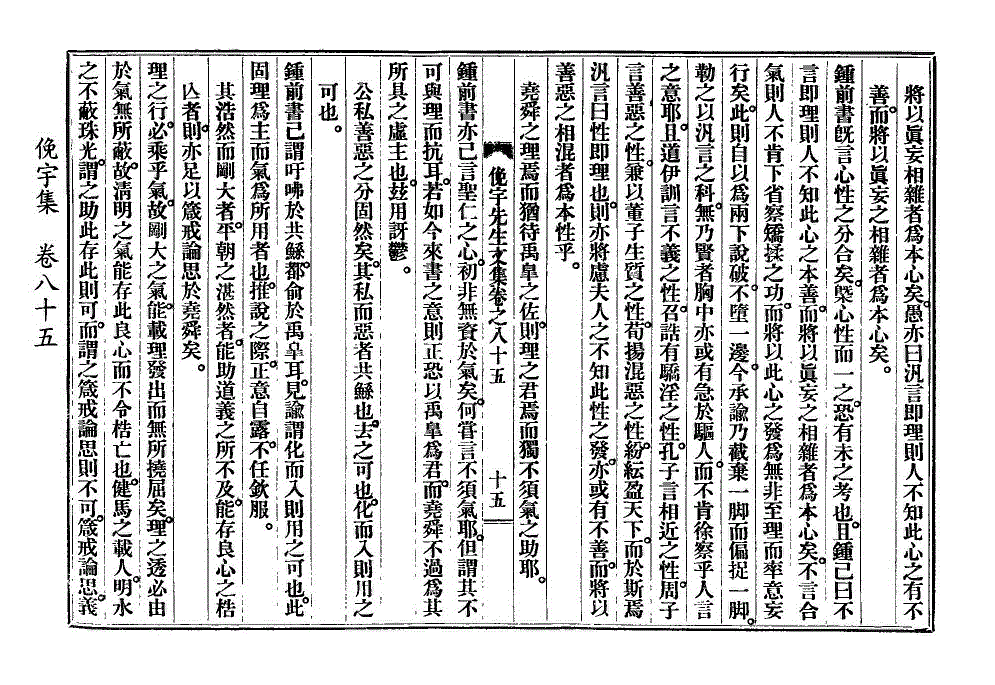 将以真妄相杂者为本心矣。愚亦曰汎言即理则人不知此心之有不善。而将以真妄之相杂者为本心矣。
将以真妄相杂者为本心矣。愚亦曰汎言即理则人不知此心之有不善。而将以真妄之相杂者为本心矣。钟前书既言心性之分合矣。槩心性而一之。恐有未之考也。且钟已曰不言即理则人不知此心之本善。而将以真妄之相杂者为本心矣。不言合气则人不肯下省察矫揉之功。而将以此心之发为无非至理而率意妄行矣。此则自以为两下说破。不堕一边。今承谕乃截弃一脚而偏捉一脚。勒之以汎言之科。无乃贤者胸中亦或有急于驱人。而不肯徐察乎人言之意耶。且道伊训言不义之性。召诰有骄淫之性。孔子言相近之性。周子言善恶之性。兼以董子生质之性。荀扬混恶之性。纷纭盈天下。而于斯焉汎言曰性即理也。则亦将虑夫人之不知此性之发。亦或有不善。而将以善恶之相混者为本性乎。
尧舜之理焉而犹待禹皋之佐。则理之君焉而独不须气之助耶。
钟前书亦已言圣仁之心。初非无资于气矣。何尝言不须气耶。但谓其不可与理而抗耳。若如今来书之意则正恐以禹皋为君。而尧舜不过为其所具之虚主也。玆用讶郁。
公私善恶之分固然矣。其私而恶者共鲧也。去之可也。化而入则用之可也。
钟前书已谓吁咈于共鲧。都俞于禹皋耳。见谕谓化而入则用之可也。此固理为主而气为所用者也。推说之际。正意自露。不任钦服。
其浩然而刚大者。平朝之湛然者。能助道义之所不及。能存良心之梏亡者。则亦足以箴戒论思于尧舜矣。
理之行。必乘乎气。故刚大之气。能载理发出而无所挠屈矣。理之透必由于气无所蔽。故清明之气能存此良心而不令梏亡也。健马之载人。明水之不蔽珠光。谓之助此存此则可。而谓之箴戒论思则不可。箴戒论思。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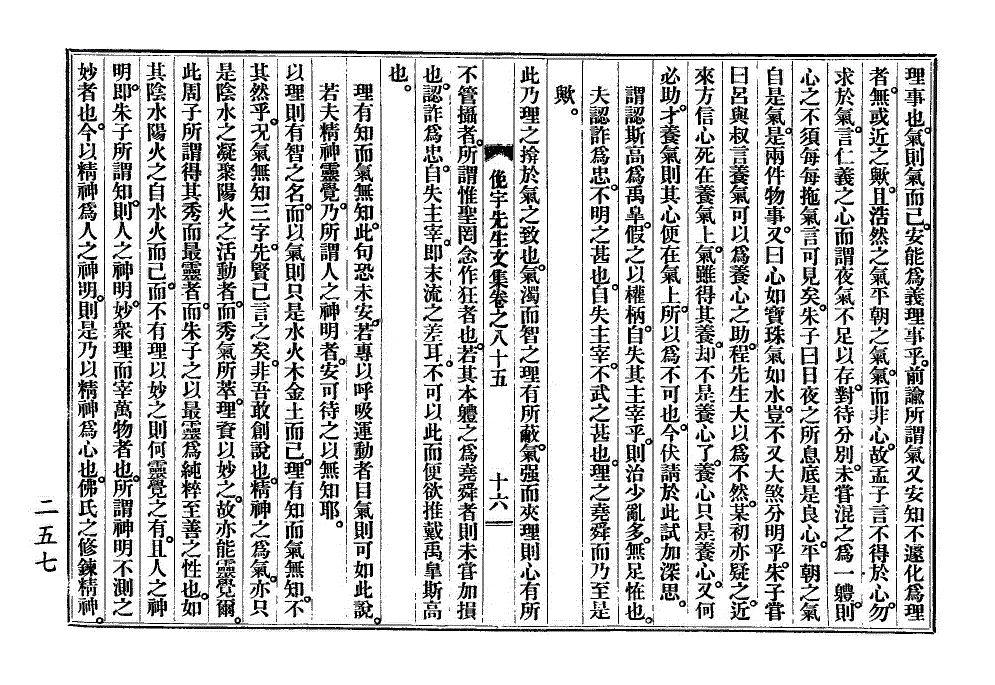 理事也。气则气而已。安能为义理事乎。前谕所谓气又安知不遽化为理者。无或近之欤。且浩然之气平朝之气。气而非心。故孟子言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言仁义之心而谓夜气不足以存。对待分别。未尝混之为一体。则心之不须每每拖气言可见矣。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朝之气自是气。是两件物事。又曰心如宝珠气如水。岂不又大煞分明乎。朱子尝曰吕与叔言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程先生大以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来方信心死在养气上。气虽得其养。却不是养心了。养心只是养心。又何必助。才养气则其心便在气上。所以为不可也。今伏请于此试加深思。
理事也。气则气而已。安能为义理事乎。前谕所谓气又安知不遽化为理者。无或近之欤。且浩然之气平朝之气。气而非心。故孟子言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言仁义之心而谓夜气不足以存。对待分别。未尝混之为一体。则心之不须每每拖气言可见矣。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朝之气自是气。是两件物事。又曰心如宝珠气如水。岂不又大煞分明乎。朱子尝曰吕与叔言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程先生大以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来方信心死在养气上。气虽得其养。却不是养心了。养心只是养心。又何必助。才养气则其心便在气上。所以为不可也。今伏请于此试加深思。谓认斯高为禹皋。假之以权柄。自失其主宰乎。则治少乱多。无足怪也。夫认诈为忠。不明之甚也。自失主宰。不武之甚也。理之尧舜而乃至是欤。
此乃理之掩于气之致也。气浊而智之理有所蔽。气强而夹理则心有所不管摄者。所谓惟圣罔念作狂者也。若其本体之为尧舜者则未尝加损也。认诈为忠。自失主宰。即末流之差耳。不可以此而便欲推戴禹皋斯高也。
理有知而气无知。此句恐未安。若专以呼吸运动者目气则可如此说。若夫精神灵觉。乃所谓人之神明者。安可待之以无知耶。
以理则有智之名。而以气则只是水火木金土而已。理有知而气无知。不其然乎。况气无知三字。先贤已言之矣。非吾敢创说也。精神之为气。亦只是阴水之凝聚阳火之活动者。而秀气所萃。理资以妙之。故亦能灵觉尔。此周子所谓得其秀而最灵者。而朱子之以最灵为纯粹至善之性也。如其阴水阳火之自水火而已。而不有理以妙之则何灵觉之有。且人之神明。即朱子所谓知。则人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所谓神明不测之妙者也。今以精神为人之神明。则是乃以精神为心也。佛氏之修鍊精神。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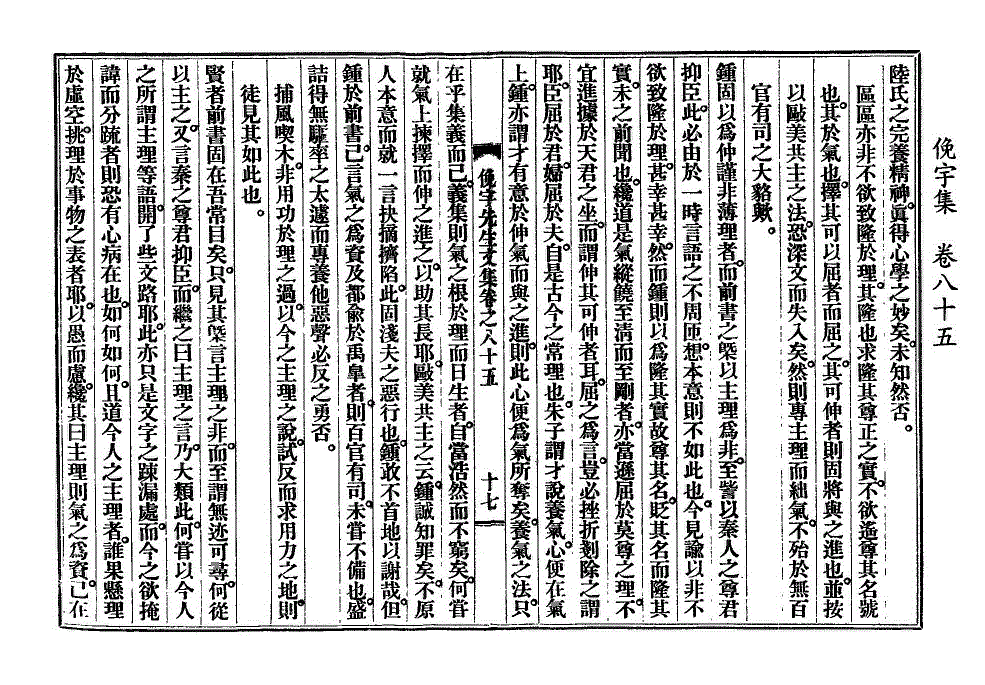 陆氏之完养精神。真得心学之妙矣。未知然否。
陆氏之完养精神。真得心学之妙矣。未知然否。区区亦非不欲致隆于理。其隆也求隆其尊正之实。不欲遥尊其名号也。其于气也。择其可以屈者而屈之。其可伸者则固将与之进也。并按以驱美共主之法。恐深文而失入矣。然则专主理而绌气。不殆于无百官有司之大貉欤。
钟固以为仲谨非薄理者。而前书之槩以主理为非。至訾以秦人之尊君抑臣。此必由于一时言语之不周匝。想本意则不如此也。今见谕以非不欲致隆于理。甚幸甚幸。然而钟则以为隆其实故尊其名。贬其名而隆其实。未之前闻也。才道是气纵饶至清而至刚者。亦当逊屈于莫尊之理。不宜进据于天君之坐。而谓伸其可伸者耳。屈之为言。岂必挫折刬除之谓耶。臣屈于君。妇屈于夫。自是古今之常理也。朱子谓才说养气。心便在气上。钟亦谓才有意于伸气而与之进。则此心便为气所夺矣。养气之法。只在乎集义而已。义集则气之根于理而日生者。自当浩然而不穷矣。何尝就气上拣择而伸之进之。以助其长耶。驱美共主之云。钟诚知罪矣。不原人本意而就一言抉摘挤陷。此固浅夫之恶行也。钟敢不首地以谢哉。但钟于前书。已言气之为资及都俞于禹皋者。则百官有司。未尝不备也。盛诘得无驱率之太遽而专养他恶声必反之勇否。
捕风吃木。非用功于理之过。以今之主理之说。试反而求用力之地。则徒见其如此也。
贤者前书固在吾常目矣。只见其槩言主理之非。而至谓无迹可寻。何从以主之。又言秦之尊君抑臣。而继之曰主理之言。乃大类此。何尝以今人之所谓主理等语。开了些文路耶。此亦只是文字之疏漏处。而今之欲掩讳而分疏者则恐有心病在也。如何如何。且道今人之主理者。谁果悬理于虚空。挑理于事物之表者耶。以愚而虑。才其曰主理则气之为资。已在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8L 页
 不言矣。若惟理而无气则一主字不已赘乎。
不言矣。若惟理而无气则一主字不已赘乎。豆稻之喻。固知其种之必获。然离土去粪。无雨露以滋之。惧不如坐而待饿也。
钟前书果有离土去粪之喻乎。有灭气绝物之云乎。岂言言而必曰种豆于土种稻于土。然后方可信豆稻之种于土耶。退陶尝曰主于践理者。气自在所养。主于养气者。气有时而灭理。旨哉言乎。明者以为然乎不然乎。
门下之极言理也。虽以曰知曰意之粗者。一归之于理之名。然则通天下凡运动而作用者皆理也。所云恍惚惊怪无位真人者。如尊见可以当之。愚不敢奉令承教矣。
知之为智之妙用。上已言之矣。性即理也。而发而为情。情乃已动之性也。初非性变而为气也。则性情只一理也。情机转而为意。意向定而为志。亦只是一理之随地头异称。不可以其乘气流行之故而便目为运动作用之气也。知觉意思。正是此心之妙别众理而裁度万事者。岂蠢然运动。矻然作用者之比耶。朱子曰性即天理也。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气者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比于他则有形器而粗者也。窃观盛意凡于心理发处。似欲一切以运动作用者区处了。如此则其所谓理者。不过为性之寂然时。而一榻之外。都不容贯通致用。以此而用功于理则其不或恍惚惊怪耶。其不为无位真人耶。鄙见之一理贯通而随地异称。正恐段落分明。地头甚实。恍惚无位之诮。姑未领解。第当自反之久而终或有悟也。
只是穷理复理。而犹必曰物曰礼者。欲其就著见有依据处用力耳。况理之无形。而必因气而著。理之不能自用。而必因气而行者乎。
易大传只言穷理。而亦非谓用力于莽旷也。事理本自合一。虽欲外事而穷之可得乎。复礼集注明言礼者天理之节文。节文固著见者。而亦只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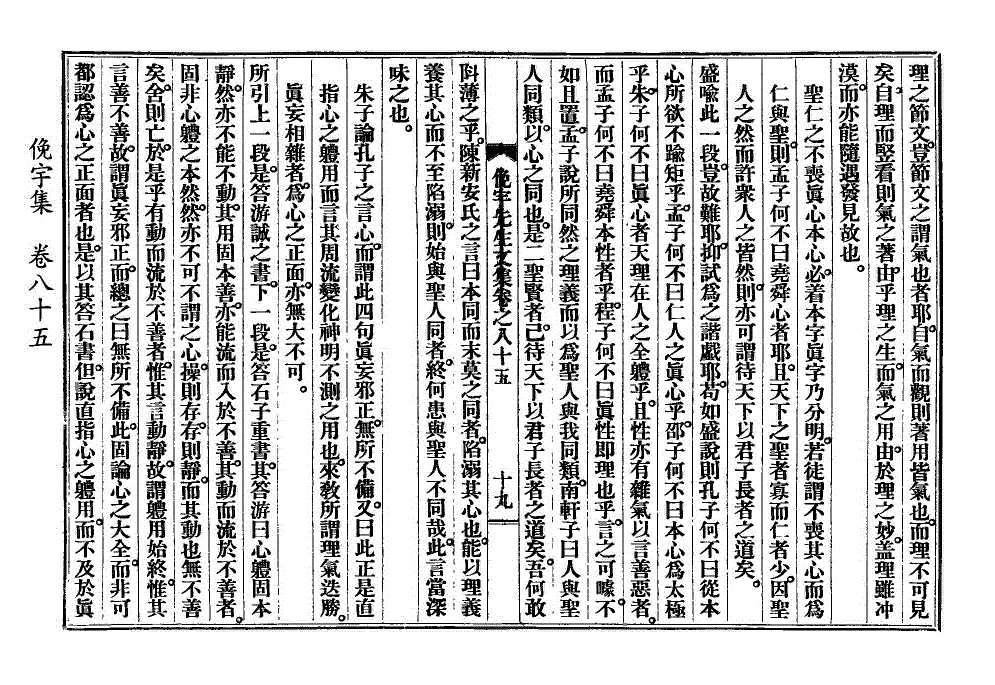 理之节文。岂节文之谓气也者耶。自气而观则著用皆气也。而理不可见矣。自理而竖看则气之著。由乎理之生。而气之用。由于理之妙。盖理虽冲漠。而亦能随遇发见故也。
理之节文。岂节文之谓气也者耶。自气而观则著用皆气也。而理不可见矣。自理而竖看则气之著。由乎理之生。而气之用。由于理之妙。盖理虽冲漠。而亦能随遇发见故也。圣仁之不丧真心本心。必着本字真字乃分明。若徒谓不丧其心而为仁与圣。则孟子何不曰尧舜心者耶。且天下之圣者寡而仁者少。因圣人之然而许众人之皆然。则亦可谓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矣。
盛喻此一段。岂故难耶。抑试为之谐戏耶。苟如盛说则孔子何不曰从本心所欲不踰矩乎。孟子何不曰仁人之真心乎。邵子何不曰本心为太极乎。朱子何不曰真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乎。且性亦有杂气以言善恶者。而孟子何不曰尧舜本性者乎。程子何不曰真性即理也乎。言之可噱。不如且置。孟子说所同然之理义而以为圣人与我同类。南轩子曰人与圣人同类。以心之同也。是二圣贤者。已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矣。吾何敢陡薄之乎。陈新安氏之言曰本同而末莫之同者。陷溺其心也。能以理义养其心而不至陷溺。则始与圣人同者。终何患与圣人不同哉。此言当深味之也。
朱子论孔子之言心。而谓此四句真妄邪正。无所不备。又曰此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用也。来教所谓理气迭胜。真妄相杂者。为心之正面。亦无大不可。
所引上一段。是答游诚之书。下一段。是答石子重书。其答游曰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其用固本善。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其动而流于不善者。固非心体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谓之心。操则存。存则静。而其动也无不善矣。舍则亡。于是乎有动而流于不善者。惟其言动静。故谓体用始终。惟其言善不善。故谓真妄邪正。而总之曰无所不备。此固论心之大全。而非可都认为心之正面者也。是以其答石书。但说直指心之体用。而不及于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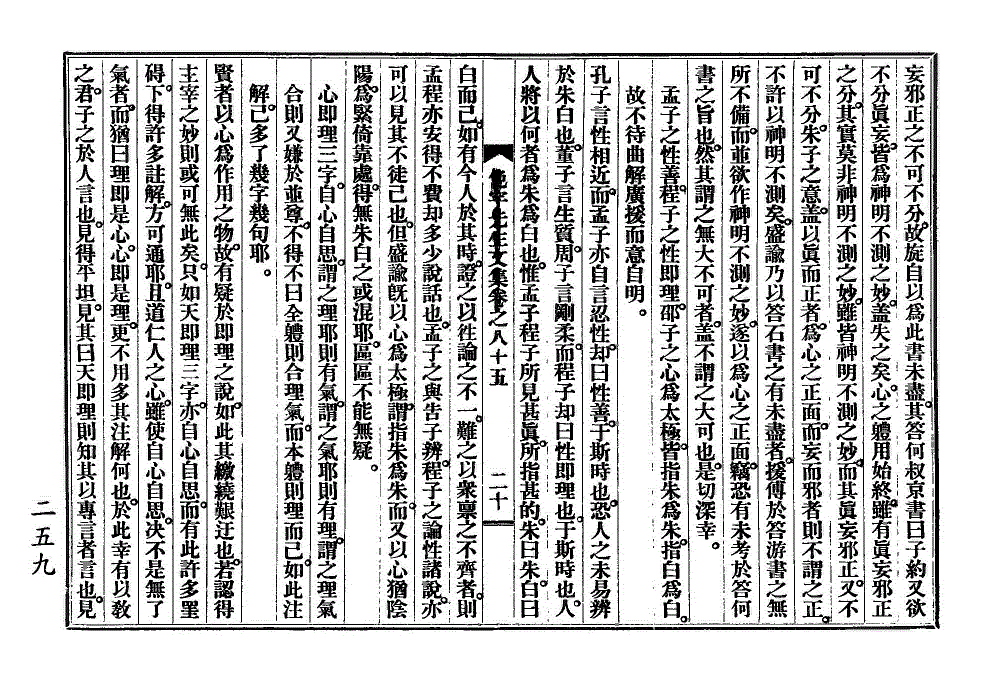 妄邪正之不可不分。故旋自以为此书未尽。其答何叔京书曰子约又欲不分真妄。皆为神明不测之妙。盖失之矣。心之体用始终。虽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实莫非神明不测之妙。虽皆神明不测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朱子之意。盖以真而正者。为心之正面。而妄而邪者则不谓之正。不许以神明不测矣。盛谕乃以答石书之有未尽者。援傅于答游书之无所不备。而并欲作神明不测之妙。遂以为心之正面。窃恐有未考于答何书之旨也。然其谓之无大不可者。盖不谓之大可也。是切深幸。
妄邪正之不可不分。故旋自以为此书未尽。其答何叔京书曰子约又欲不分真妄。皆为神明不测之妙。盖失之矣。心之体用始终。虽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实莫非神明不测之妙。虽皆神明不测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朱子之意。盖以真而正者。为心之正面。而妄而邪者则不谓之正。不许以神明不测矣。盛谕乃以答石书之有未尽者。援傅于答游书之无所不备。而并欲作神明不测之妙。遂以为心之正面。窃恐有未考于答何书之旨也。然其谓之无大不可者。盖不谓之大可也。是切深幸。孟子之性善。程子之性即理。邵子之心为太极。皆指朱为朱。指白为白。故不待曲解广援而意自明。
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亦自言忍性。却曰性善。于斯时也。恐人之未易辨于朱白也。董子言生质。周子言刚柔。而程子却曰性即理也。于斯时也。人人将以何者为朱为白也。惟孟子程子所见甚真。所指甚的。朱曰朱。白曰白而已。如有今人于其时。證之以往论之不一。难之以众禀之不齐者。则孟程亦安得不费却多少说话也。孟子之与告子辨。程子之论性诸说。亦可以见其不徒已也。但盛谕既以心为太极。谓指朱为朱。而又以心犹阴阳。为紧倚靠处。得无朱白之或混耶。区区不能无疑。
心即理三字。自心自思。谓之理耶则有气。谓之气耶则有理。谓之理气合则又嫌于并尊。不得不曰全体则合理气。而本体则理而已。如此注解。已多了几字几句耶。
贤者以心为作用之物。故有疑于即理之说。如此其缴绕艰迂也。若认得主宰之妙则或可无此矣。只如天即理三字。亦自心自思。而有此许多挂碍。下得许多注解。方可通耶。且道仁人之心。虽使自心自思。决不是无了气者。而犹曰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更不用多其注解何也。于此幸有以教之。君子之于人言也。见得平坦。见其曰天即理则知其以专言者言也。见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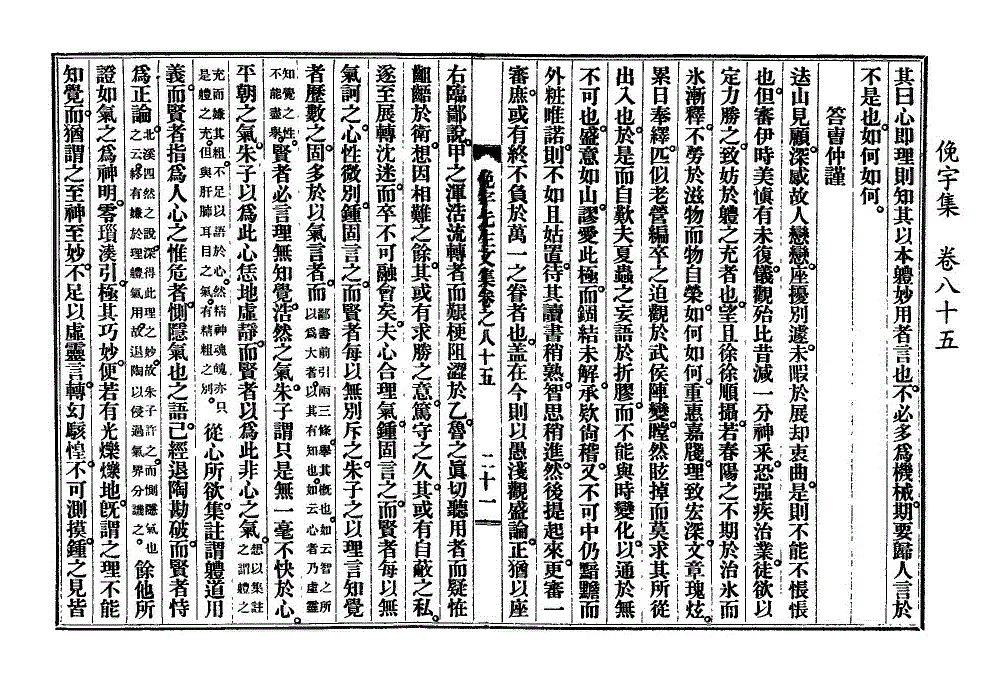 其曰心即理则知其以本体妙用者言也。不必多为机械。期要归人言于不是也。如何如何。
其曰心即理则知其以本体妙用者言也。不必多为机械。期要归人言于不是也。如何如何。答曹仲谨
迲山见顾。深感故人恋恋。座扰别遽。未暇于展却衷曲。是则不能不怅怅也。但审伊时美慎有未复。仪观殆比昔减一分神采。恐强疾治业。徒欲以定力胜之。致妨于体之充者也。望且徐徐顺摄。若春阳之不期于治冰而冰渐释。不劳于滋物而物自荣。如何如何。重惠嘉笺。理致宏深。文章瑰炫。累日奉绎。匹似老营编卒之迫观于武侯阵变。瞠然眩掉而莫求其所从出入也。于是而自叹夫夏虫之妄语于折胶。而不能与时变化。以通于无不可也。盛意如山。谬爱此极。而锢结未解。承款尚稽。又不可中仍黯黵而外妆唯诺。则不如且姑置。待其读书稍熟。智思稍进。然后提起来。更审一审。庶或有终不负于万一之眷者也。盖在今则以愚浅观盛论。正犹以座右临鄙说。甲之浑浩流转者而艰梗阻涩于乙。鲁之真切听用者而疑怪龃龉于卫。想因相难之馀。其或有求胜之意。笃守之久。其或有自蔽之私。遂至展转沈迷。而卒不可融会矣。夫心合理气。钟固言之。而贤者每以无气诃之。心性微别。钟固言之。而贤者每以无别斥之。朱子之以理言知觉者历数之。固多于以气言者。而(鄙书前引两三条。举其概也。如云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有知也。如云心者乃虚灵知觉之性。不能尽举。)贤者必言理无知觉。浩然之气。朱子谓只是无一毫不快于心。平朝之气。朱子以为此心恁地虚静。而贤者以为此非心之气。(想以集注之谓体之充而嫌其粗。不足以语于心。然精神魂魄亦只是体之充。但与肝肺耳目之气。有精粗之别。)从心所欲。集注谓体道用义。而贤者指为人心之惟危者。恻隐气也之语。已经退陶勘破。而贤者恃为正论。(北溪四然之说。深得此理之妙。故朱子许之。而恻隐气也之云。终有嫌于理体气用。故退陶以侵过气界分讥之。)馀他所證如气之为神明。零琐凑引。极其巧妙。便若有光烁烁地。既谓之理不能知觉。而犹谓之至神至妙。不足以虚灵言。转幻骇惶。不可测摸。钟之见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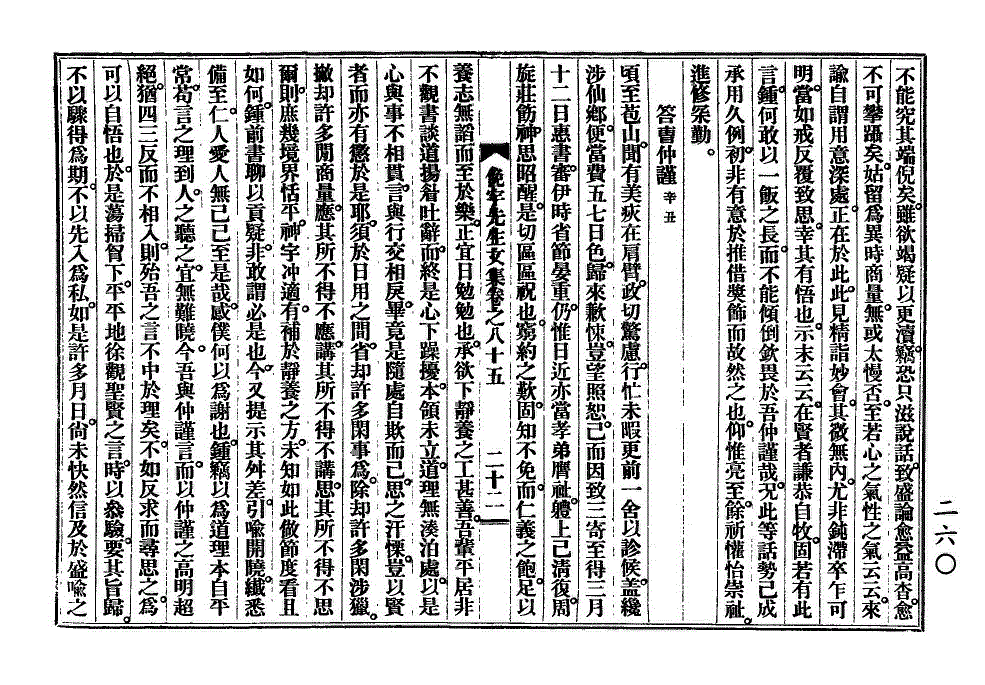 不能究其端倪矣。虽欲竭疑以更渎。窃恐只滋说话。致盛论愈益高杳。愈不可攀蹑矣。姑留为异时商量。无或太慢否。至若心之气性之气云云。来谕自谓用意深处。正在于此。此见精诣妙会。其微无内。尤非钝滞卒乍可明。当如戒反覆致思。幸其有悟也。示末云云。在贤者谦恭自牧。固若有此言。钟何敢以一饭之长。而不能倾倒钦畏于吾仲谨哉。况此等话势已成承用久例。初非有意于推借奖饰而故然之也。仰惟亮至。馀祈欢怡崇祉。进修深勤。
不能究其端倪矣。虽欲竭疑以更渎。窃恐只滋说话。致盛论愈益高杳。愈不可攀蹑矣。姑留为异时商量。无或太慢否。至若心之气性之气云云。来谕自谓用意深处。正在于此。此见精诣妙会。其微无内。尤非钝滞卒乍可明。当如戒反覆致思。幸其有悟也。示末云云。在贤者谦恭自牧。固若有此言。钟何敢以一饭之长。而不能倾倒钦畏于吾仲谨哉。况此等话势已成承用久例。初非有意于推借奖饰而故然之也。仰惟亮至。馀祈欢怡崇祉。进修深勤。答曹仲谨(辛丑)
顷至苞山。闻有美疢在肩臂。政切惊虑。行忙未暇更前一舍以诊候。盖才涉仙乡。便当费五七日色。归来歉悚。岂望照恕。已而因致三寄至得三月十二日惠书。审伊时省节晏重。仍惟日近亦当孝弟膺祉。体上已清复。周旋庄饬。神思昭醒。是切区区祝也。穷约之叹。固知不免。而仁义之饱。足以养志无谄而至于乐。正宜日勉勉也。承欲下静养之工甚善。吾辈平居非不观书谈道扬眉吐辞。而终是心下躁扰。本领未立。道理无凑泊处。以是心与事不相贯。言与行交相戾。毕竟是随处自欺而已。思之汗慄。岂以贤者而亦有惩于是耶。须于日用之间。省却许多闲事为。除却许多闲涉猎。撇却许多閒商量。应其所不得不应。讲其所不得不讲。思其所不得不思尔。则庶几境界恬平。神宇冲适。有补于静养之方。未知如此做节度看且如何。钟前书聊以贡疑。非敢谓必是也。今又提示其舛差。引喻开晓。纤悉备至。仁人爱人无已已至是哉。感仆何以为谢也。钟窃以为道理本自平常。苟言之理到。人之听之。宜无难晓。今吾与仲谨言。而以仲谨之高明超绝。犹四三反而不相入。则殆吾之言不中于理矣。不如反求而寻思之。为可以自悟也。于是荡扫胸下。平平地徐观圣贤之言。时以参验。要其旨归。不以骤得为期。不以先入为私。如是许多月日。尚未快然信及于盛喻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1H 页
 加。钝根之难拔何此甚也。是以今于来教。亦不能无疑。盖所谓心者虚灵知觉之性。既是心性一理之谓。则于此何曾有由气知觉而性无虚灵之意耶。极说所谓最灵指言心也。而朱子又曰最灵者纯粹至善之性。果何也。其曰圣人者能言之天。曰孔明有忠义之司马懿。明者真以心与性为若人天地(一作之)二物葛马之两人耶。是未可知也。心之体固是理。而动而为气所掩则于是乎有踰于矩者。圣人则自志学以至耳顺。真积力久。气融私泯。故动静惟一而莫非至理。若曰任气自用而自然听命于理。则心是气而理为心外之主宰。以其自然听命而可曰即理。则孝顺之子。可曰子即父。都俞之臣。可曰臣即君矣。声为律而身为度。设譬之辞也。体即道用即义。直指之言也。心之理。即性之理也。而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理可谓无欲乎。心之理。理之体也。而矩则乃此理之限度也。理动而不踰乎限度。何疑于叠床也。反覆究绎。只见盛说之外若捷巧而内实浅碎。有不敢遽会者。钟之愚至此极矣。奈何奈何。近日之留心于径捷殊绝。而低看他稍近下有据依处。是诚可忧也。钟窃观从古高明者之乐于径捷殊绝。而陷于禅会者。类多是弄得精爽神通妙圆。持以自喜。不肯放舍。遂至以理为障。其于民彝物则平常当行之理。则犹恐其一经于心而乱吾之真。其故诚何由哉。愚则曰人之本心即理也。故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者。全其本心也。众人之心每流于气汩者。亦不可不谓之心。然失其本心者。君子当不心焉。为心学者求复其本心而已。本心复则气之为运用之资者。自在所养。而不患于馁而死矣。幸仲谨之重教之也。然而吾年尚未耆耋。容可以再思自新。亦有以宽贷而徐俟之则幸甚。馀祈欢履加护。
加。钝根之难拔何此甚也。是以今于来教。亦不能无疑。盖所谓心者虚灵知觉之性。既是心性一理之谓。则于此何曾有由气知觉而性无虚灵之意耶。极说所谓最灵指言心也。而朱子又曰最灵者纯粹至善之性。果何也。其曰圣人者能言之天。曰孔明有忠义之司马懿。明者真以心与性为若人天地(一作之)二物葛马之两人耶。是未可知也。心之体固是理。而动而为气所掩则于是乎有踰于矩者。圣人则自志学以至耳顺。真积力久。气融私泯。故动静惟一而莫非至理。若曰任气自用而自然听命于理。则心是气而理为心外之主宰。以其自然听命而可曰即理。则孝顺之子。可曰子即父。都俞之臣。可曰臣即君矣。声为律而身为度。设譬之辞也。体即道用即义。直指之言也。心之理。即性之理也。而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理可谓无欲乎。心之理。理之体也。而矩则乃此理之限度也。理动而不踰乎限度。何疑于叠床也。反覆究绎。只见盛说之外若捷巧而内实浅碎。有不敢遽会者。钟之愚至此极矣。奈何奈何。近日之留心于径捷殊绝。而低看他稍近下有据依处。是诚可忧也。钟窃观从古高明者之乐于径捷殊绝。而陷于禅会者。类多是弄得精爽神通妙圆。持以自喜。不肯放舍。遂至以理为障。其于民彝物则平常当行之理。则犹恐其一经于心而乱吾之真。其故诚何由哉。愚则曰人之本心即理也。故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者。全其本心也。众人之心每流于气汩者。亦不可不谓之心。然失其本心者。君子当不心焉。为心学者求复其本心而已。本心复则气之为运用之资者。自在所养。而不患于馁而死矣。幸仲谨之重教之也。然而吾年尚未耆耋。容可以再思自新。亦有以宽贷而徐俟之则幸甚。馀祈欢履加护。答曹仲谨
前月因南行至箭村。惠书之七月发者已见抵矣。披复数三。深感贤者之终始眷眷于无状至此也。旅里卒卒。无暇修覆。归来月已冬矣。不审欢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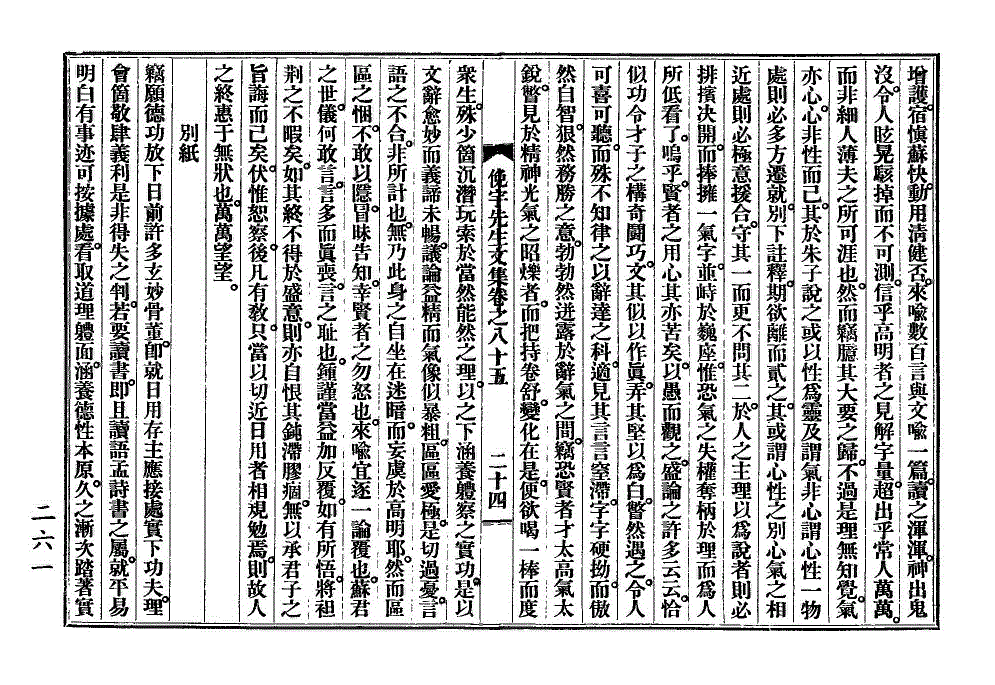 增护。宿慎苏快。动用清健否。来喻数百言与文喻一篇。读之浑浑。神出鬼没。令人眩晃骇掉而不可测。信乎高明者之见解宇量。超出乎常人万万。而非细人薄夫之所可涯也。然而窃臆其大要之归。不过是理无知觉。气亦心。心非性而已。其于朱子说之或以性为灵及谓气非心谓心性一物处则必多方迁就。别下注释。期欲离而贰之。其或谓心性之别心气之相近处则必极意援合。守其一而更不问其二。于人之主理以为说者则必排摈决开。而捧拥一气字。并峙于巍座。惟恐气之失权夺柄于理而为人所低看了。呜乎。贤者之用心其亦苦矣。以愚而观之。盛论之许多云云。恰似功令才子之构奇斗巧。文其似以作真。弄其坚以为白。瞥然遇之。令人可喜可听。而殊不知律之以辞达之科。适见其言言窒滞。字字硬拗。而傲然自智。狠然务胜之意。勃勃然迸露于辞气之间。窃恐贤者才太高气太锐。瞥见于精神光气之昭烁者。而把持卷舒。变化在是。便欲喝一棒而度众生。殊少个沉潜玩索于当然能然之理。以之下涵养体察之实功。是以文辞愈妙而义谛未畅。议论益精而气像似暴粗。区区爱极。是切过忧。言语之不合。非所计也。无乃此身之自坐在迷暗。而妄虞于高明耶。然而区区之悃。不敢以隐。冒昧告知。幸贤者之勿怒也。来喻宜逐一论覆也。苏君之世。仪何敢言。言多而真丧。言之耻也。钟谨当益加反覆。如有所悟。将袒荆之不暇矣。如其终不得于盛意。则亦自恨其钝滞胶痼。无以承君子之旨诲而已矣。伏惟恕察。后凡有教。只当以切近日用者相规勉焉。则故人之终惠于无状也。万万望望。
增护。宿慎苏快。动用清健否。来喻数百言与文喻一篇。读之浑浑。神出鬼没。令人眩晃骇掉而不可测。信乎高明者之见解宇量。超出乎常人万万。而非细人薄夫之所可涯也。然而窃臆其大要之归。不过是理无知觉。气亦心。心非性而已。其于朱子说之或以性为灵及谓气非心谓心性一物处则必多方迁就。别下注释。期欲离而贰之。其或谓心性之别心气之相近处则必极意援合。守其一而更不问其二。于人之主理以为说者则必排摈决开。而捧拥一气字。并峙于巍座。惟恐气之失权夺柄于理而为人所低看了。呜乎。贤者之用心其亦苦矣。以愚而观之。盛论之许多云云。恰似功令才子之构奇斗巧。文其似以作真。弄其坚以为白。瞥然遇之。令人可喜可听。而殊不知律之以辞达之科。适见其言言窒滞。字字硬拗。而傲然自智。狠然务胜之意。勃勃然迸露于辞气之间。窃恐贤者才太高气太锐。瞥见于精神光气之昭烁者。而把持卷舒。变化在是。便欲喝一棒而度众生。殊少个沉潜玩索于当然能然之理。以之下涵养体察之实功。是以文辞愈妙而义谛未畅。议论益精而气像似暴粗。区区爱极。是切过忧。言语之不合。非所计也。无乃此身之自坐在迷暗。而妄虞于高明耶。然而区区之悃。不敢以隐。冒昧告知。幸贤者之勿怒也。来喻宜逐一论覆也。苏君之世。仪何敢言。言多而真丧。言之耻也。钟谨当益加反覆。如有所悟。将袒荆之不暇矣。如其终不得于盛意。则亦自恨其钝滞胶痼。无以承君子之旨诲而已矣。伏惟恕察。后凡有教。只当以切近日用者相规勉焉。则故人之终惠于无状也。万万望望。别纸
窃愿德功放下日前许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应接处实下功夫。理会个敬肆义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读书。即且读语孟诗书之属。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据处。看取道理体面。涵养德性本原。久之渐次踏著实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2H 页
 地。即此等说话。须自见得黑白。不须如此劳心费力矣。若必欲便穷竟此说。亦请先罢穿凿己见。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说与德功不同者。并合两家。写作一处。子细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诘。亦庶几有究竟处。不至如今日只见一边不相照应。而信口信笔。无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怀不能已。略此奉报。千万详之。若以为是。幸即加功。若以为非。即此书不烦见答。今后不须更下喻矣。
地。即此等说话。须自见得黑白。不须如此劳心费力矣。若必欲便穷竟此说。亦请先罢穿凿己见。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说与德功不同者。并合两家。写作一处。子细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诘。亦庶几有究竟处。不至如今日只见一边不相照应。而信口信笔。无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怀不能已。略此奉报。千万详之。若以为是。幸即加功。若以为非。即此书不烦见答。今后不须更下喻矣。右朱先生答江德功书也。偶尔阅此。有感于心。聊以录呈。区区窃欲从事于此书所戒也。虽贤者恐亦不可不省于此也。如何如何。
答曹仲谨(壬寅)
昨间因灵川寄至正月惠书。恭审伊时欢节崇禧。想今亦对序加重矣。钟月前有从兄之丧。悲痛不可言。前者数度往复。固知其断断出于相爱之赤衷。而钝根滞甚。尚不能奉教以周旋。则无宁彼此权行倚阁。徐徐讲究于他端。或冀其有所触悟而可抵烂漫。故顷有所云云尔。至如辞气之凌厉。钟非怒其逼已。但在贤者降气修辞之道。谓不宜至此耳。邪正之际。不得不然。虽使贤者有是言。亦何伤也。任之而已。久当自返。钟未尝为此敖惰骄矜之辞。承喻惶忸。不知所以自鸣也。第谓名义与工夫。初无二致。惟名义如此。故工夫必如此。苟名义如彼而工夫乃如此。则是名实之相戾。而正名之不足贵也。况文是载道之器。而以文喻心则心之为物。只是轮辕之类。以此为名义之得正。果信乎。惟其认心为器而理为其所载而已。故虽盛说之张皇震耀。滂沛不穷。而命意一差。全体辟盭。此所以敢道它言言窒滞字字硬拗。而不虞其见怪于明者也。切近日用。固非在于心外。然心学之要。专在于察其念之善恶。审其事之是非。敬谨以持之。诚实以行之而已。曷尝费精于心体之是理是气。竞辩于理气之是心是性。而强其所不及知。躐其所不及到。认以为了此。即是心学之单方乎。所谓心得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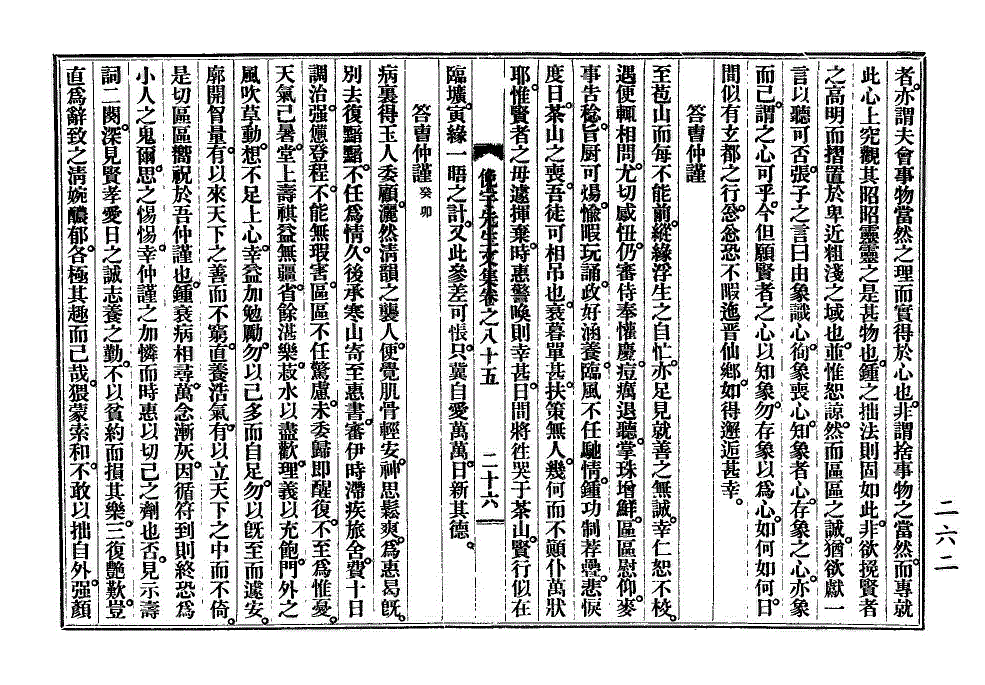 者。亦谓夫会事物当然之理而实得于心也。非谓舍事物之当然。而专就此心上究观其昭昭灵灵之是甚物也。钟之拙法则固如此。非欲挽贤者之高明而摺置于卑近粗浅之域也。并惟恕谅。然而区区之诚。犹欲献一言以听可否。张子之言曰由象识心。徇象丧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今但愿贤者之心以知象。勿存象以为心。如何如何。日间似有玄都之行。匆匆恐不暇迤晋仙乡。如得邂逅甚幸。
者。亦谓夫会事物当然之理而实得于心也。非谓舍事物之当然。而专就此心上究观其昭昭灵灵之是甚物也。钟之拙法则固如此。非欲挽贤者之高明而摺置于卑近粗浅之域也。并惟恕谅。然而区区之诚。犹欲献一言以听可否。张子之言曰由象识心。徇象丧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今但愿贤者之心以知象。勿存象以为心。如何如何。日间似有玄都之行。匆匆恐不暇迤晋仙乡。如得邂逅甚幸。答曹仲谨
至苞山而每不能前。纵缘浮生之自忙。亦足见就善之无诚。幸仁恕不校。遇便辄相问。尤切感忸。仍审侍奉欢庆。痘疠退听。掌珠增鲜。区区慰仰。麦事告稔。旨厨可炀。愉暇玩诵。政好涵养。临风不任驰情。钟功制荐叠。悲悷度日。茶山之丧。吾徒可相吊也。衰暮单甚。扶策无人。几何而不颠仆万状耶。惟贤者之毋遽挥弃。时惠警唤则幸甚。日间将往哭于茶山。贤行似在临圹。寅缘一晤之计。又此参差可怅。只冀自爱万万。日新其德。
答曹仲谨(癸卯)
病里得玉人委顾。洒然清韵之袭人。便觉肌骨轻安。神思松爽。为惠曷既。别去复黯黯。不任为情。久后承寒山寄至惠书。审伊时滞疾旅舍。费十日调治。强惫登程。不能无瑕害。区区不任惊虑。未委归即醒复。不至为惟忧。天气已暑。堂上寿祺益无疆。省馀湛乐。菽水以尽欢。理义以充饱。门外之风吹草动。想不足上心。幸益加勉励。勿以已多而自足。勿以既至而遽安。廓开胸量。有以来天下之善而不穷。直养浩气。有以立天下之中而不倚。是切区区向祝于吾仲谨也。钟衰病相寻。万念渐灰。因循符到则终恐为小人之鬼尔。思之惕惕。幸仲谨之加怜而时惠以切已之剂也否。见示寿词二阕。深见贤孝爱日之诚志养之勤。不以贫约而损其乐。三复艳叹。岂直为辞致之清婉醲郁。各极其趣而已哉。猥蒙索和。不敢以拙自外。强颜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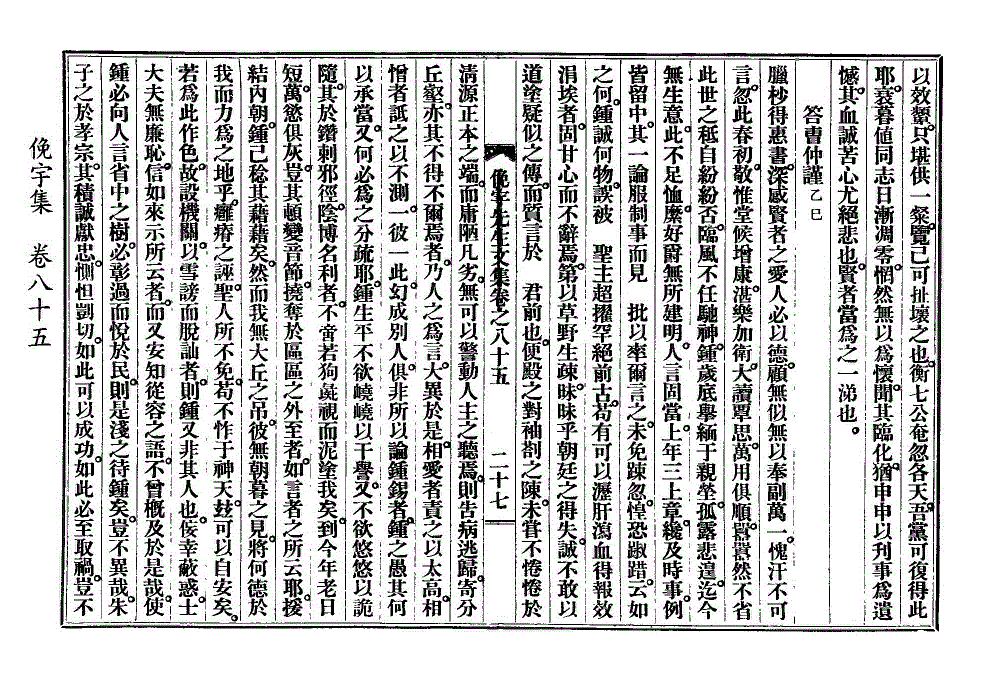 以效颦。只堪供一粲。览已可扯坏之也。衡七公奄忽各天。吾党可复得此耶。衰暮值同志日渐凋零。惘然无以为怀。闻其临化。犹申申以刊事为遗憾。其血诚苦心尤绝悲也。贤者当为之一涕也。
以效颦。只堪供一粲。览已可扯坏之也。衡七公奄忽各天。吾党可复得此耶。衰暮值同志日渐凋零。惘然无以为怀。闻其临化。犹申申以刊事为遗憾。其血诚苦心尤绝悲也。贤者当为之一涕也。答曹仲谨(乙巳)
腊杪得惠书。深感贤者之爱人必以德。顾无似无以奉副万一。愧汗不可言。忽此春初。敬惟堂候增康。湛乐加卫。大读覃思。万用俱顺。嚣嚣然不省此世之秪自纷纷否。临风不任驰神。钟岁底举缅于亲茔。孤露悲遑。迄今无生意。此不足恤。縻好爵无所建明。人言固当。上年三上章。才及时事。例皆留中。其一论服制事而见 批以率尔言之。未免疏忽。惶恐踧踖。云如之何。钟诚何物。误被 圣主超擢罕绝前古。苟有可以沥肝泻血得报效涓埃者。固甘心而不辞焉。第以草野生疏。昧昧乎朝廷之得失。诚不敢以道涂疑似之传。而质言于 君前也。便殿之对袖劄之陈。未尝不惓惓于清源正本之端。而庸陋凡劣。无可以警动人主之听焉。则告病逃归。寄分丘壑。亦其不得不尔焉者。乃人之为言。大异于是。相爱者责之以太高。相憎者诋之以不测。一彼一此。幻成别人。俱非所以论钟锡者。钟之愚其何以承当。又何必为之分疏耶。钟生平不欲峣峣以干誉。又不欲悠悠以诡随。其于钻刺邪径。阴博名利者。不啻若狗彘视而泥涂我矣。到今年老日短。万欲俱灰。岂其顿变音节。挠夺于区区之外至者。如言者之所云耶。援结内朝。钟已稔其藉藉矣。然而我无大丘之吊。彼无朝暮之见。将何德于我而力为之地乎。痈瘠之诬。圣人所不免。苟不怍于神天。玆可以自安矣。若为此作色。故设机关。以雪谤而脱讪者。则钟又非其人也。佞幸蔽惑。士大夫无廉耻。信如来示所云者。而又安知从容之语。不曾概及于是哉。使钟必向人言省中之树。必彰过而悦于民。则是浅之待钟矣。岂不异哉。朱子之于孝宗。其积诚献忠。恻怛剀切。如此可以成功。如此必至取祸。岂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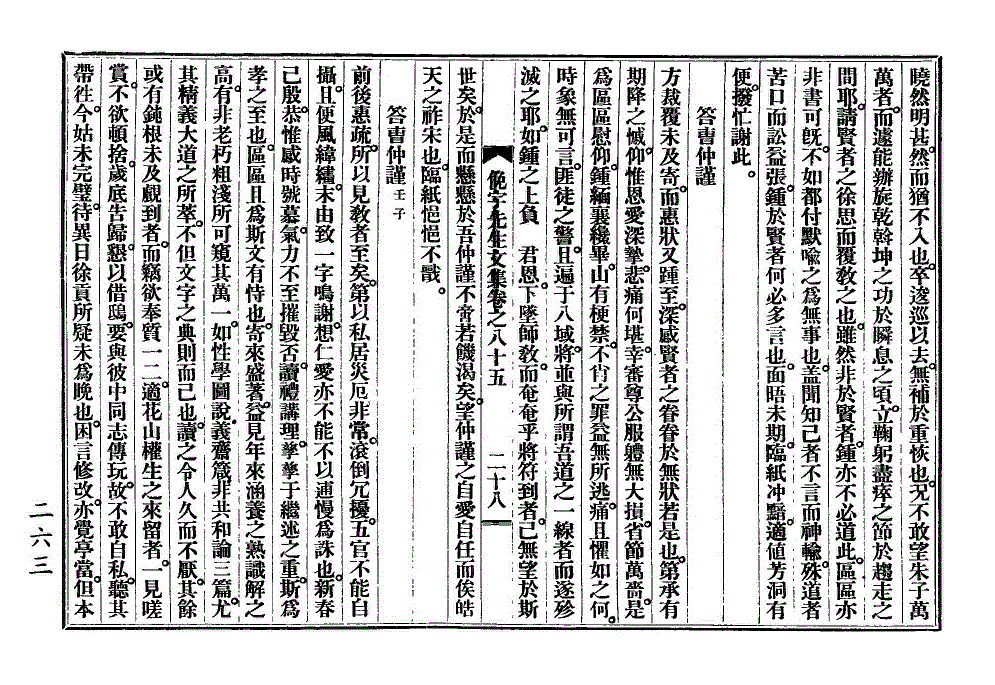 晓然明甚。然而犹不入也。卒逡巡以去。无补于重恢也。况不敢望朱子万万者。而遽能办旋乾斡坤之功于瞬息之顷。立鞠躬尽瘁之节于趋走之间耶。请贤者之徐思而覆教之也。虽然非于贤者。钟亦不必道此。区区亦非书可既。不如都付默喻之为无事也。盖闻知己者不言而神输。殊道者苦口而讼益张。钟于贤者何必多言也。面晤未期。临纸冲黯。适值芳洞有便。拨忙谢此。
晓然明甚。然而犹不入也。卒逡巡以去。无补于重恢也。况不敢望朱子万万者。而遽能办旋乾斡坤之功于瞬息之顷。立鞠躬尽瘁之节于趋走之间耶。请贤者之徐思而覆教之也。虽然非于贤者。钟亦不必道此。区区亦非书可既。不如都付默喻之为无事也。盖闻知己者不言而神输。殊道者苦口而讼益张。钟于贤者何必多言也。面晤未期。临纸冲黯。适值芳洞有便。拨忙谢此。答曹仲谨
方裁覆未及寄。而惠状又踵至。深感贤者之眷眷于无状若是也。第承有期降之戚。仰惟恩爱深挚。悲痛何堪。幸审尊公服体无大损。省节万啬。是为区区慰仰。钟缅襄才毕。山有梗禁。不肖之罪益无所逃。痛且惧如之何。时象无可言。匪徒之警。且遍于八域。将并与所谓吾道之一线者而遂殄灭之耶。如钟之上负 君恩。下坠师教。而奄奄乎将符到者。已无望于斯世矣。于是而悬悬于吾仲谨不啻若饥渴矣。望仲谨之自爱自任而俟皓天之祚宋也。临纸悒悒不戬。
答曹仲谨(壬子)
前后惠疏。所以见教者至矣。第以私居灾厄非常。滚倒冗扰。五官不能自摄。且便风纬繣。末由致一字鸣谢。想仁爱亦不能不以逋慢为诛也。新春已殷。恭惟感时号慕。气力不至摧毁否。读礼讲理。孳孳于继述之重。斯为孝之至也。区区且为斯文有恃也。寄来盛著。益见年来涵养之熟识解之高。有非老朽粗浅所可窥其万一。如性学图说,义斋箴非共和论三篇。尤其精义大道之所萃。不但文字之典则而已也。读之令人久而不厌。其馀或有钝根未及觑到者。而窃欲奉质一二。适花山权生之来留者。一见嗟赏。不欲顿舍。岁底告归。恳以借鸱。要与彼中同志传玩。故不敢自私。听其带往。今姑未完璧。待异日徐贡所疑未为晚也。困言修改。亦觉亭当。但本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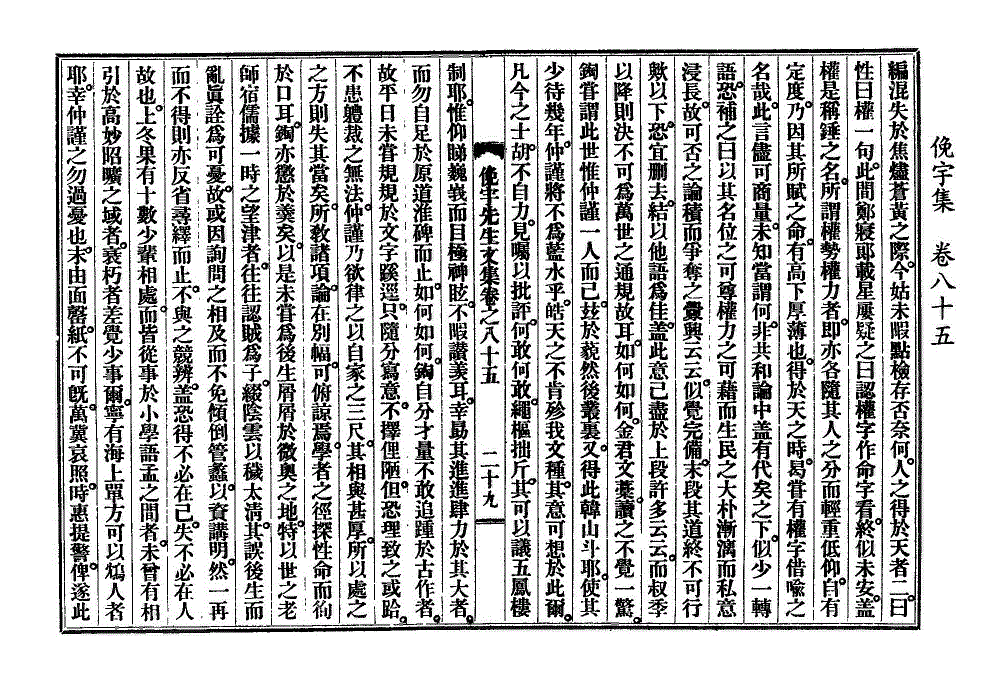 编混失于焦烬苍黄之际。今姑未暇点检存否奈何。人之得于天者二。曰性曰权一句。此间郑寝郎载星屡疑之曰认权字作命字看。终似未安。盖权是称锤之名。所谓权势权力者。即亦各随其人之分而轻重低仰。自有定度。乃因其所赋之命。有高下厚薄也。得于天之时。曷尝有权字借喻之名哉。此言尽可商量。未知当谓何。非共和论中盖有代矣之下。似少一转语。恐补之曰以其名位之可尊权力之可藉而生民之大朴渐漓而私意浸长。故可否之论积而争夺之衅兴云云。似觉完备。末段其道终不可行欤以下。恐宜删去。结以他语为佳。盖此意已尽于上段许多云云。而叔季以降则决不可为万世之通规故耳。如何如何。金君文藁。读之不觉一惊。鋾尝谓此世惟仲谨一人而已。玆于藐然后丛里。又得此韩山斗耶。使其少待几年。仲谨将不为蓝水乎。皓天之不肯殄我文种。其意可想于此尔。凡今之士。胡不自力。见嘱以批评。何敢何敢。绳枢拙斤。其可以议五凤楼制耶。惟仰睇巍峨而目极神眩。不暇赞羡耳。幸勖其进进肆力于其大者。而勿自足于原道淮碑而止。如何如何。鋾自分才量不敢追踵于古作者。故平日未尝规规于文字蹊径。只随分写意。不择俚陋。但恐理致之或跲。不患体裁之无法。仲谨乃欲律之以自家之三尺。其相与甚厚。所以处之之方则失其当矣。所教诸项。论在别幅。可俯谅焉。学者之径探性命而徇于口耳。鋾亦惩于羹矣。以是未尝为后生屑屑于微奥之地。特以世之老师宿儒据一时之望津者。往往认贼为子。缀阴云以秽太清。其误后生而乱真诠为可忧。故或因询问之相及而不免倾倒管蠡。以资讲明。然一再而不得则亦反省寻绎而止。不与之竞辨。盖恐得不必在己。失不必在人故也。上冬果有十数少辈相处。而皆从事于小学语孟之间者。未曾有相引于高妙昭旷之域者。衰朽者差觉少事尔。宁有海上单方可以鸩人者耶。幸仲谨之勿过忧也。末由面罄。纸不可既。万冀哀照。时惠提警。俾遂此
编混失于焦烬苍黄之际。今姑未暇点检存否奈何。人之得于天者二。曰性曰权一句。此间郑寝郎载星屡疑之曰认权字作命字看。终似未安。盖权是称锤之名。所谓权势权力者。即亦各随其人之分而轻重低仰。自有定度。乃因其所赋之命。有高下厚薄也。得于天之时。曷尝有权字借喻之名哉。此言尽可商量。未知当谓何。非共和论中盖有代矣之下。似少一转语。恐补之曰以其名位之可尊权力之可藉而生民之大朴渐漓而私意浸长。故可否之论积而争夺之衅兴云云。似觉完备。末段其道终不可行欤以下。恐宜删去。结以他语为佳。盖此意已尽于上段许多云云。而叔季以降则决不可为万世之通规故耳。如何如何。金君文藁。读之不觉一惊。鋾尝谓此世惟仲谨一人而已。玆于藐然后丛里。又得此韩山斗耶。使其少待几年。仲谨将不为蓝水乎。皓天之不肯殄我文种。其意可想于此尔。凡今之士。胡不自力。见嘱以批评。何敢何敢。绳枢拙斤。其可以议五凤楼制耶。惟仰睇巍峨而目极神眩。不暇赞羡耳。幸勖其进进肆力于其大者。而勿自足于原道淮碑而止。如何如何。鋾自分才量不敢追踵于古作者。故平日未尝规规于文字蹊径。只随分写意。不择俚陋。但恐理致之或跲。不患体裁之无法。仲谨乃欲律之以自家之三尺。其相与甚厚。所以处之之方则失其当矣。所教诸项。论在别幅。可俯谅焉。学者之径探性命而徇于口耳。鋾亦惩于羹矣。以是未尝为后生屑屑于微奥之地。特以世之老师宿儒据一时之望津者。往往认贼为子。缀阴云以秽太清。其误后生而乱真诠为可忧。故或因询问之相及而不免倾倒管蠡。以资讲明。然一再而不得则亦反省寻绎而止。不与之竞辨。盖恐得不必在己。失不必在人故也。上冬果有十数少辈相处。而皆从事于小学语孟之间者。未曾有相引于高妙昭旷之域者。衰朽者差觉少事尔。宁有海上单方可以鸩人者耶。幸仲谨之勿过忧也。末由面罄。纸不可既。万冀哀照。时惠提警。俾遂此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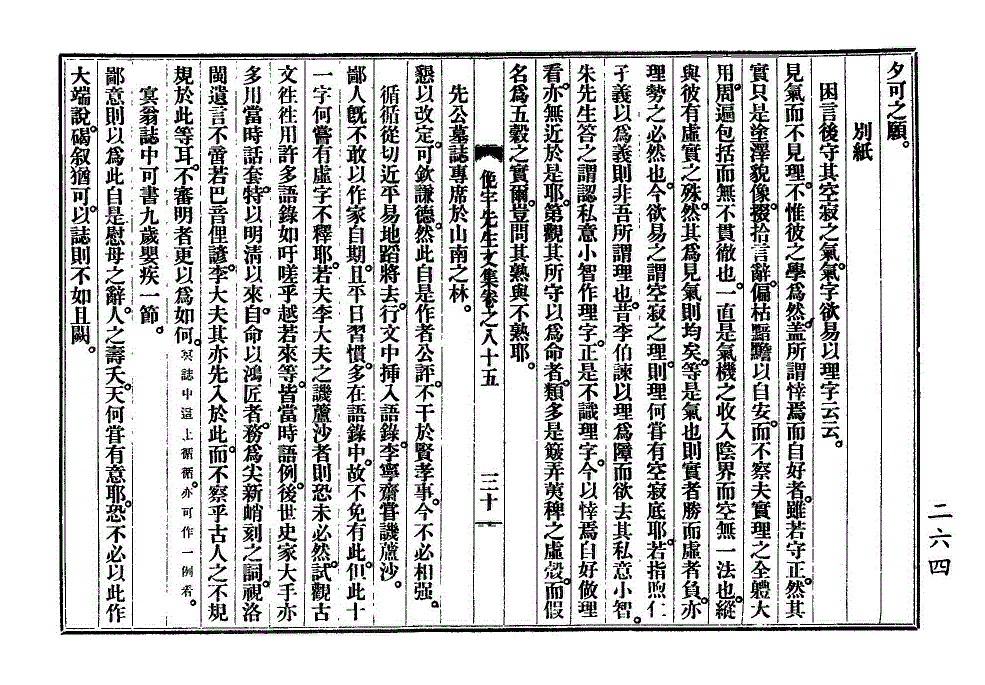 夕可之愿。
夕可之愿。别纸
困言后守其空寂之气。气字欲易以理字云云。
见气而不见理。不惟彼之学为然。盖所谓悻焉。而自好者。虽若守正。然其实只是涂泽貌像。掇拾言辞。偏枯黯黵以自安。而不察夫实理之全体大用。周遍包括而无不贯彻也。一直是气机之收入阴界而空无一法也。纵与彼有虚实之殊。然其为见气则均矣。等是气也则实者胜而虚者负。亦理势之必然也。今欲易之谓空寂之理。则理何尝有空寂底耶。若指煦仁孑义以为义则非吾所谓理也。昔李伯谏以理为障而欲去其私意小智。朱先生答之谓认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识理字。今以悻焉自好做理看。亦无近于是耶。第观其所守以为命者。类多是簸弄荑稗之虚壳。而假名为五谷之实尔。岂问其熟与不熟耶。
先公墓志专席于山南之林。
恳以改定。可钦谦德。然此自是作者公评。不干于贤孝事。今不必相强。
循循从切近平易地蹈将去。行文中插入语录。李宁斋尝讥芦沙。
鄙人既不敢以作家自期。且平日习惯。多在语录中。故不免有此。但此十一字何尝有虚字不释耶。若夫李大夫之讥芦沙者则恐未必然。试观古文往往用许多语录如吁嗟乎越若来等。皆当时语例。后世史家大手亦多用当时话套。特以明清以来。自命以鸿匠者。务为尖新峭刻之词。视洛闽遗言不啻若巴音俚谚。李大夫其亦先入于此。而不察乎古人之不规规于此等耳。不审明者更以为如何。(冥志中这上循循。亦可作一例看。)
冥翁志中可书九岁婴疾一节。
鄙意则以为此自是慰母之辞。人之寿夭。天何尝有意耶。恐不必以此作大端说。碣叙犹可。以志则不如且阙。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八十五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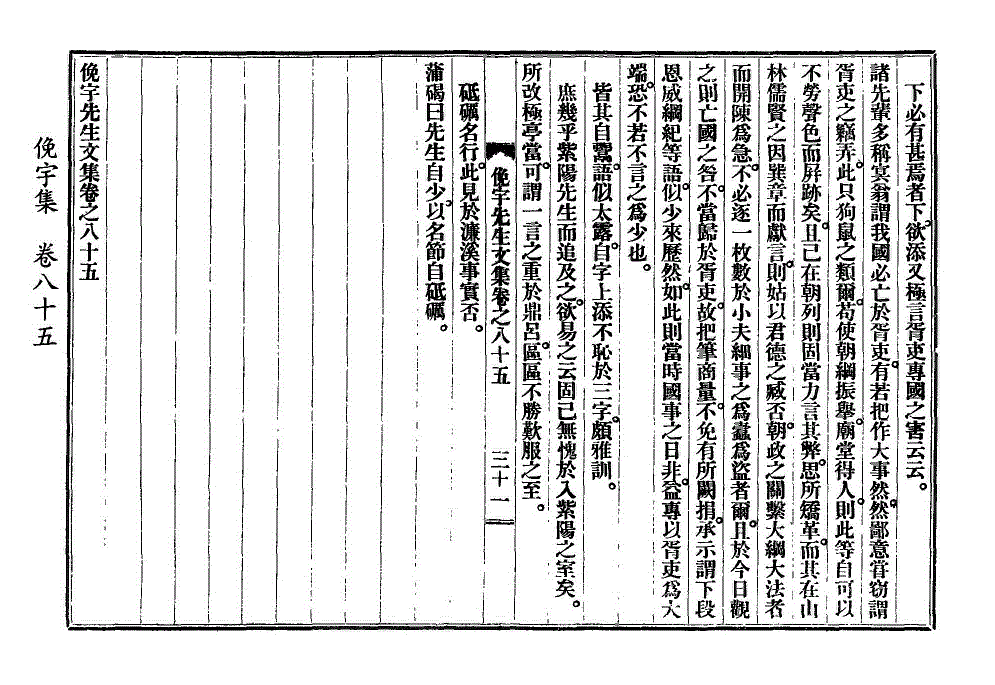 下必有甚焉者下。欲添又极言胥吏专国之害云云。
下必有甚焉者下。欲添又极言胥吏专国之害云云。诸先辈多称冥翁谓我国必亡于胥吏。有若把作大事然。然鄙意尝窃谓胥吏之窃弄。此只狗鼠之类尔。苟使朝纲振举。庙堂得人。则此等自可以不劳声色而屏迹矣。且已在朝列则固当力言其弊。思所矫革。而其在山林儒贤之因巽章而献言。则姑以君德之臧否。朝政之关系大纲大法者而开陈为急。不必逐一枚数于小夫细事之为蠹为盗者尔。且于今日观之则亡国之咎。不当归于胥吏。故把笔商量。不免有所阙捐。承示谓下段恩威纲纪等语。似少来历然。如此则当时国事之日非。益专以胥吏为大端。恐不若不言之为少也。
皆其自鬻。语似太露。自字上添不耻于三字。颇雅训。
庶几乎紫阳先生而追及之。欲易之云固已无愧于入紫阳之室矣。
所改极亭当。可谓一言之重于鼎吕。区区不胜叹服之至。
砥砺名行。此见于濂溪事实否。
蒲碣曰先生自少。以名节自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