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书
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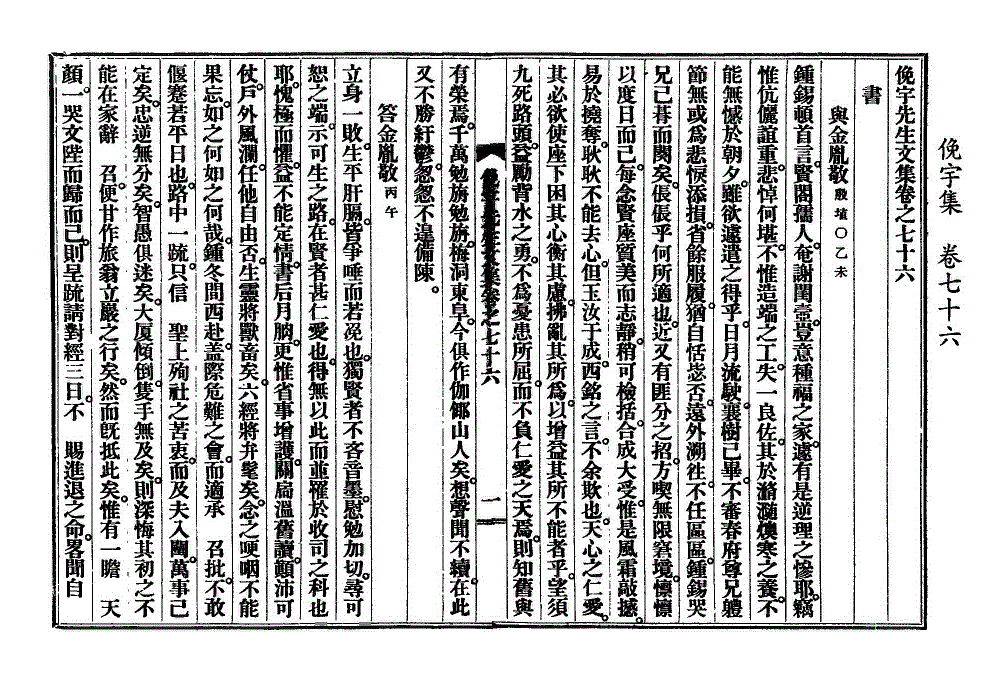 与金胤敬(殷埴○乙未)
与金胤敬(殷埴○乙未)钟锡顿首言。贤閤孺人。奄谢闺壸。岂意种福之家。遽有是逆理之惨耶。窃惟伉俪谊重。悲悼何堪。不惟造端之工。失一良佐。其于滫瀡燠寒之养。不能无憾于朝夕。虽欲遽遣之得乎。日月流驶。襄树已毕。不审春府尊兄体节无或为悲悷添损。省馀服履。犹自恬毖否。远外溯往。不任区区。钟锡哭兄已期而阕矣。伥伥乎何所适也。近又有匪分之招。方吃无限窘境。懔懔以度日而已。每念贤座质美而志静。稍可检括。合成大受。惟是风霜敲撼。易于挠夺。耿耿不能去心。但玉汝于成。西铭之言。不余欺也。天心之仁爱。其必欲使座下困其心衡其虑。拂乱其所为。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乎。望须九死路头。益励背水之勇。不为忧患所屈。而不负仁爱之天焉。则知旧与有荣焉。千万勉旃勉旃。梅洞东阜。今俱作伽倻山人矣。想声闻不续。在此又不胜纡郁。匆匆不遑备陈。
答金胤敬(丙午)
立身一败。生平肝膈。皆争唾而若浼也。独贤者不吝音墨。慰勉加切。寻可恕之端。示可生之路。在贤者甚仁爱也。得无以此而并罹于收司之科也耶。愧极而惧。益不能定情。书后月朒。更惟省事增护。关扃温旧读。颠沛可仗。户外风澜。任他自由否。生灵将兽畜矣。六经将弁髦矣。念之哽咽不能果忘。如之何如之何哉。钟冬间西赴。盖际危难之会。而适承 召批。不敢偃蹇若平日也。路中一疏。只信 圣上殉社之苦衷。而及夫入闉。万事已定矣。忠逆无分矣。智愚俱迷矣。大厦倾倒。只手无及矣。则深悔其初之不能在家辞 召。便甘作旅翁立岩之行矣。然而既抵此矣。惟有一瞻 天颜。一哭文陛而归而已。则呈疏请对经三日。不 赐进退之命。略闻自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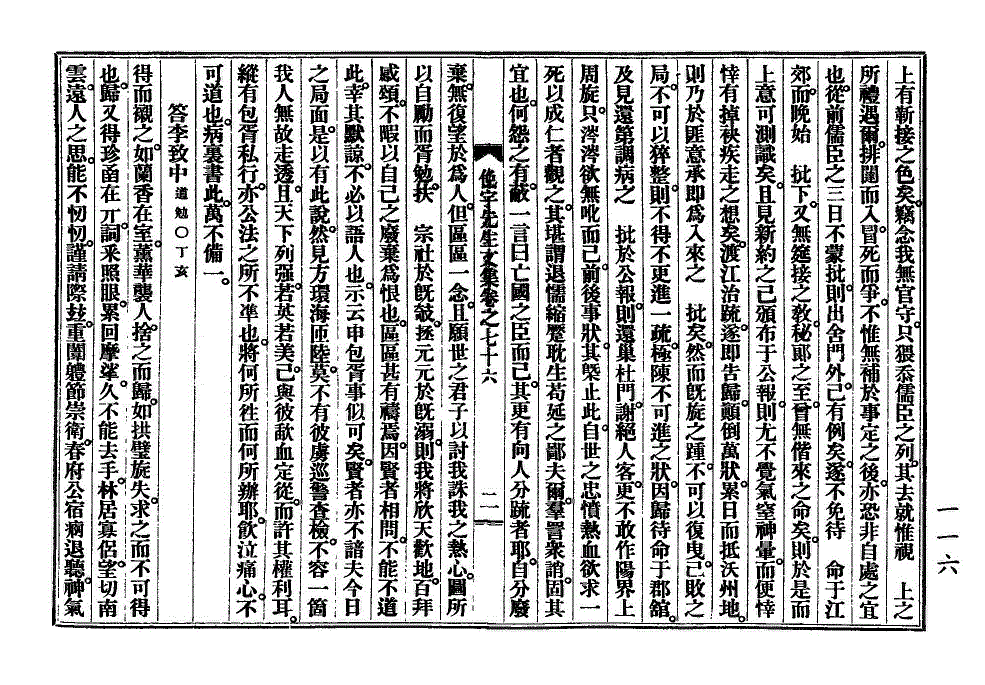 上有靳接之色矣。窃念我无官守。只猥忝儒臣之列。其去就惟视 上之所礼遇尔。排闼而入。冒死而争。不惟无补于事定之后。亦恐非自处之宜也。从前儒臣之三日不蒙批。则出舍门外。已有例矣。遂不免待 命于江郊。而晚始 批下。又无筵接之教。秘郎之至。曾无偕来之命矣。则于是而上意可测识矣。且见新约之已颁布于公报。则尤不觉气窒神晕。而便悻悻有掉袂疾走之想矣。渡江治疏。遂即告归。颠倒万状。累日而抵沃州地。则乃于匪意承即为入来之 批矣。然而既旋之踵。不可以复曳。已败之局。不可以猝整。则不得不更进一疏。极陈不可进之状。因归待命于郡馆。及见还第调病之 批于公报。则还巢杜门。谢绝人客。更不敢作阳界上周旋。只涔涔欲无吪而已。前后事状。其槩止此。自世之忠愤热血欲求一死以成仁者观之。其堪谓退懦缩蹶(一作蹙)耽生苟延之鄙夫尔。群詈众诮。固其宜也。何怨之有。蔽一言曰亡国之臣而已。其更有向人分疏者耶。自分废弃。无复望于为人。但区区一念。且愿世之君子以讨我诛我之热心。图所以自励而胥勉。扶 宗社于既攲。拯元元于既溺。则我将欣天欢地。百拜感颂。不暇以自己之废弃为恨也。区区甚有祷焉。因贤者相问。不能不道此。幸其默谅。不必以语人也。示云申包胥事似可矣。贤者亦不谙夫今日之局面。是以有此说。然见方环海匝陆。莫不有彼虏巡警查检。不容一个我人无故走透。且天下列强。若英若美。已与彼歃血定从。而许其权利耳。纵有包胥私行。亦公法之所不准也。将何所往而何所办耶。饮泣痛心。不可道也。病里书此。万不备一。
上有靳接之色矣。窃念我无官守。只猥忝儒臣之列。其去就惟视 上之所礼遇尔。排闼而入。冒死而争。不惟无补于事定之后。亦恐非自处之宜也。从前儒臣之三日不蒙批。则出舍门外。已有例矣。遂不免待 命于江郊。而晚始 批下。又无筵接之教。秘郎之至。曾无偕来之命矣。则于是而上意可测识矣。且见新约之已颁布于公报。则尤不觉气窒神晕。而便悻悻有掉袂疾走之想矣。渡江治疏。遂即告归。颠倒万状。累日而抵沃州地。则乃于匪意承即为入来之 批矣。然而既旋之踵。不可以复曳。已败之局。不可以猝整。则不得不更进一疏。极陈不可进之状。因归待命于郡馆。及见还第调病之 批于公报。则还巢杜门。谢绝人客。更不敢作阳界上周旋。只涔涔欲无吪而已。前后事状。其槩止此。自世之忠愤热血欲求一死以成仁者观之。其堪谓退懦缩蹶(一作蹙)耽生苟延之鄙夫尔。群詈众诮。固其宜也。何怨之有。蔽一言曰亡国之臣而已。其更有向人分疏者耶。自分废弃。无复望于为人。但区区一念。且愿世之君子以讨我诛我之热心。图所以自励而胥勉。扶 宗社于既攲。拯元元于既溺。则我将欣天欢地。百拜感颂。不暇以自己之废弃为恨也。区区甚有祷焉。因贤者相问。不能不道此。幸其默谅。不必以语人也。示云申包胥事似可矣。贤者亦不谙夫今日之局面。是以有此说。然见方环海匝陆。莫不有彼虏巡警查检。不容一个我人无故走透。且天下列强。若英若美。已与彼歃血定从。而许其权利耳。纵有包胥私行。亦公法之所不准也。将何所往而何所办耶。饮泣痛心。不可道也。病里书此。万不备一。答李致中(道勉○丁亥)
得而衬之。如兰香在室。薰华袭人。舍之而归。如拱璧旋失。求之而不可得也。归又得珍函在丌。词采照眼。累回摩挲。久不能去手。林居寡侣。望切南云。远人之思。能不忉忉。谨请际玆。重闱体节崇卫。春府公宿痾退听。神气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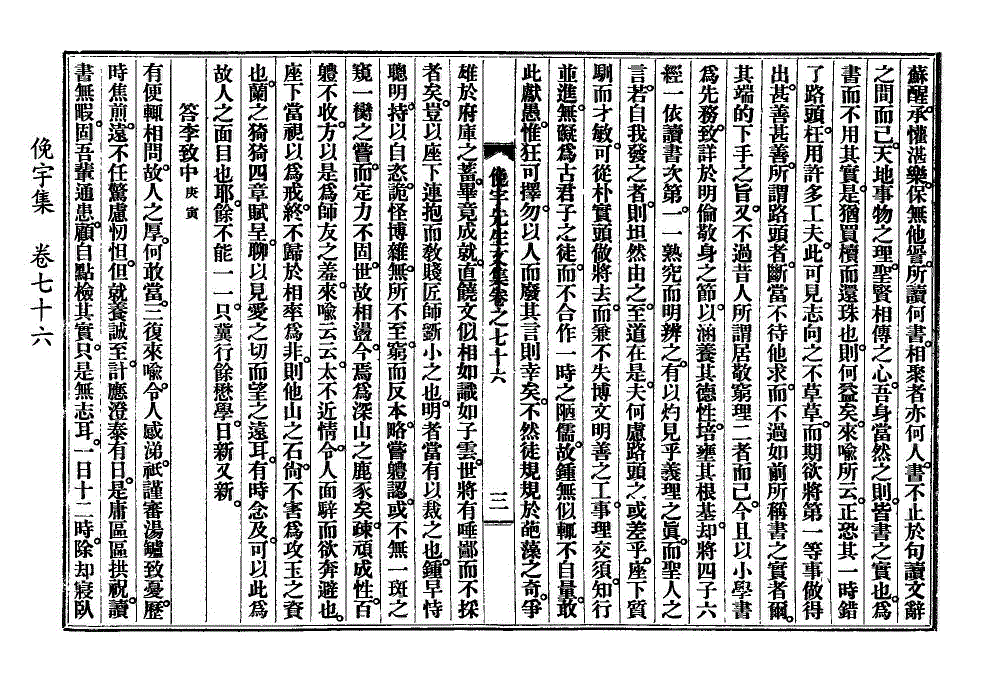 苏醒。承欢湛乐。保无他愆。所读何书。相聚者亦何人。书不止于句读文辞之间而已。天地事物之理。圣贤相传之心。吾身当然之则。皆书之实也。为书而不用其实。是犹买椟而还珠也。则何益矣。来喻所云。正恐其一时错了路头。枉用许多工夫。此可见志向之不草草。而期欲将第一等事做得出。甚善甚善。所谓路头者。断当不待他求。而不过如前所称书之实者尔。其端的下手之旨。又不过昔人所谓居敬穷理二者而已。今且以小学书为先务。致详于明伦敬身之节。以涵养其德性。培壅其根基。却将四子六经一依读书次第。一一熟究而明辨之。有以灼见乎义理之真。而圣人之言。若自我发之者。则坦然由之。至道在是。夫何虑路头之或差乎。座下质驯而才敏。可从朴实头做将去。而兼不失博文明善之工。事理交须。知行并进。无碍为古君子之徒。而不合作一时之陋儒。故钟无似辄不自量。敢此献愚。惟狂可择。勿以人而废其言则幸矣。不然徒规规于葩藻之奇。争雄于府库之蓄。毕竟成就。直饶文似相如识如子云。世将有唾鄙而不采者矣。岂以座下连抱而教贱匠师斲小之也。明者当有以裁之也。钟早恃聪明。持以自恣。诡怪博杂。无所不至。穷而反本。略尝体认。或不无一斑之窥一脔之尝。而定力不固。世故相荡。今焉为深山之鹿豕矣。疏顽成性。百体不收。方以是为师友之羞。来喻云云。太不近情。令人面骍而欲奔避也。座下当视以为戒。终不归于相率为非。则他山之石。尚不害为攻玉之资也。兰之猗猗四章赋呈。聊以见爱之切而望之远耳。有时念及。可以此为故人之面目也耶。馀不能一一。只冀行馀懋学。日新又新。
苏醒。承欢湛乐。保无他愆。所读何书。相聚者亦何人。书不止于句读文辞之间而已。天地事物之理。圣贤相传之心。吾身当然之则。皆书之实也。为书而不用其实。是犹买椟而还珠也。则何益矣。来喻所云。正恐其一时错了路头。枉用许多工夫。此可见志向之不草草。而期欲将第一等事做得出。甚善甚善。所谓路头者。断当不待他求。而不过如前所称书之实者尔。其端的下手之旨。又不过昔人所谓居敬穷理二者而已。今且以小学书为先务。致详于明伦敬身之节。以涵养其德性。培壅其根基。却将四子六经一依读书次第。一一熟究而明辨之。有以灼见乎义理之真。而圣人之言。若自我发之者。则坦然由之。至道在是。夫何虑路头之或差乎。座下质驯而才敏。可从朴实头做将去。而兼不失博文明善之工。事理交须。知行并进。无碍为古君子之徒。而不合作一时之陋儒。故钟无似辄不自量。敢此献愚。惟狂可择。勿以人而废其言则幸矣。不然徒规规于葩藻之奇。争雄于府库之蓄。毕竟成就。直饶文似相如识如子云。世将有唾鄙而不采者矣。岂以座下连抱而教贱匠师斲小之也。明者当有以裁之也。钟早恃聪明。持以自恣。诡怪博杂。无所不至。穷而反本。略尝体认。或不无一斑之窥一脔之尝。而定力不固。世故相荡。今焉为深山之鹿豕矣。疏顽成性。百体不收。方以是为师友之羞。来喻云云。太不近情。令人面骍而欲奔避也。座下当视以为戒。终不归于相率为非。则他山之石。尚不害为攻玉之资也。兰之猗猗四章赋呈。聊以见爱之切而望之远耳。有时念及。可以此为故人之面目也耶。馀不能一一。只冀行馀懋学。日新又新。答李致中(庚寅)
有便辄相问。故人之厚。何敢当。三复来喻。令人感涕。祇谨审汤垆致忧。历时焦煎。远不任惊虑忉怛。但就养诚至。计应澄泰有日。是庸区区拱祝。读书无暇。固吾辈通患。顾自点检其实。只是无志耳。一日十二时。除却寝卧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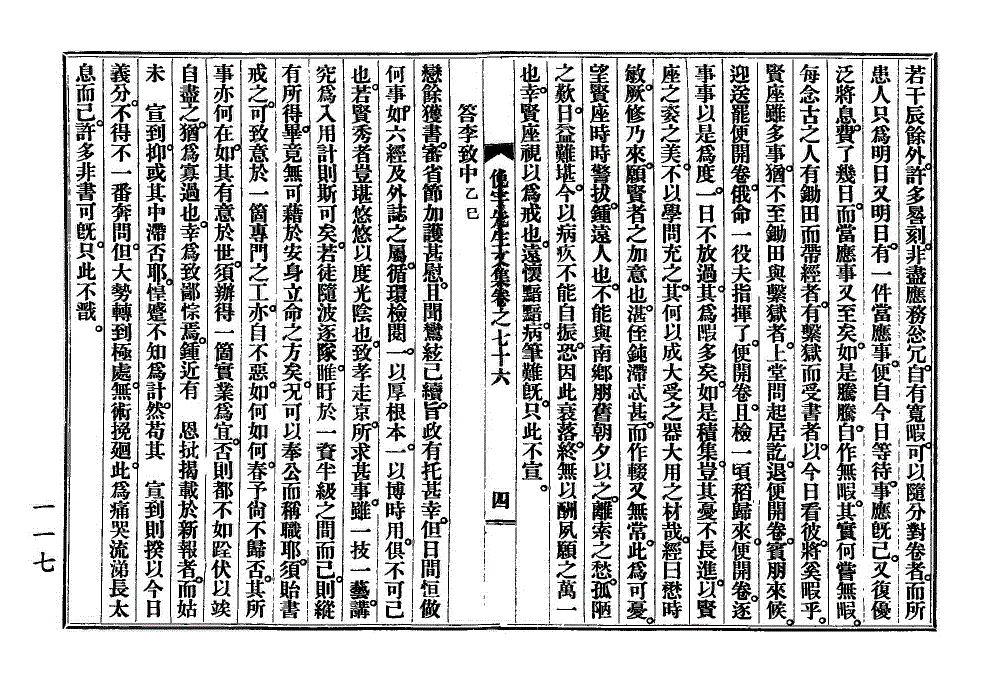 若干辰馀外。许多晷刻。非尽应务匆冗。自有宽暇。可以随分对卷者。而所患人只为明日又明日。有一件当应事。便自今日等待。事应既已。又复优泛将息。费了几日。而当应事又至矣。如是腾腾。自作无暇。其实何尝无暇。每念古之人有锄田而带经者。有系狱而受书者。以今日看彼。将奚暇乎。贤座虽多事。犹不至锄田与系狱者。上堂问起居讫。退便开卷。宾朋来候。迎送罢便开卷。俄命一役夫指挥了。便开卷。且检一顷稻归来。便开卷。逐事事以是为度。一日不放过。其为暇多矣。如是积集。岂其忧不长进。以贤座之姿之美。不以学问充之。其何以成大受之器大用之材哉。经曰懋时敏。厥修乃来。愿贤者之加意也。湛侄钝滞忒甚。而作辍又无常。此为可忧。望贤座时时警拔。钟远人也。不能与南乡朋旧朝夕以之。离索之愁。孤陋之叹。日益难堪。今以病疚不能自振。恐因此衰落。终无以酬夙愿之万一也。幸贤座视以为戒也。远怀黯黯。病笔难既。只此不宣。
若干辰馀外。许多晷刻。非尽应务匆冗。自有宽暇。可以随分对卷者。而所患人只为明日又明日。有一件当应事。便自今日等待。事应既已。又复优泛将息。费了几日。而当应事又至矣。如是腾腾。自作无暇。其实何尝无暇。每念古之人有锄田而带经者。有系狱而受书者。以今日看彼。将奚暇乎。贤座虽多事。犹不至锄田与系狱者。上堂问起居讫。退便开卷。宾朋来候。迎送罢便开卷。俄命一役夫指挥了。便开卷。且检一顷稻归来。便开卷。逐事事以是为度。一日不放过。其为暇多矣。如是积集。岂其忧不长进。以贤座之姿之美。不以学问充之。其何以成大受之器大用之材哉。经曰懋时敏。厥修乃来。愿贤者之加意也。湛侄钝滞忒甚。而作辍又无常。此为可忧。望贤座时时警拔。钟远人也。不能与南乡朋旧朝夕以之。离索之愁。孤陋之叹。日益难堪。今以病疚不能自振。恐因此衰落。终无以酬夙愿之万一也。幸贤座视以为戒也。远怀黯黯。病笔难既。只此不宣。答李致中(乙巳)
恋馀获书。审省节加护甚慰。且闻鸾弦已续。旨政有托甚幸。但日间恒做何事。如六经及外志之属。循环检阅。一以厚根本。一以博时用。俱不可已也。若贤秀者岂堪悠悠以度光阴也。致孝走京。所求甚事。虽一技一艺。讲究为入用计则斯可矣。若徒随波逐队。睢盱于一资半级之间而已。则纵有所得。毕竟无可藉于安身立命之方矣。况可以奉公而称职耶。须贻书戒之。可致意于一个专门之工。亦自不恶。如何如何。春予尚不归否。其所事亦何在。如其有意于世。须办得一个实业为宜。否则都不如跧伏以俟自尽之。犹为寡过也。幸为致鄙悰焉。钟近有 恩批揭载于新报者。而姑未 宣到。抑或其中滞否耶。惶蹙不知为计。然苟其 宣到则揆以今日义分。不得不一番奔问。但大势转到极处。无术挽回。此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许多非书可既。只此不戬。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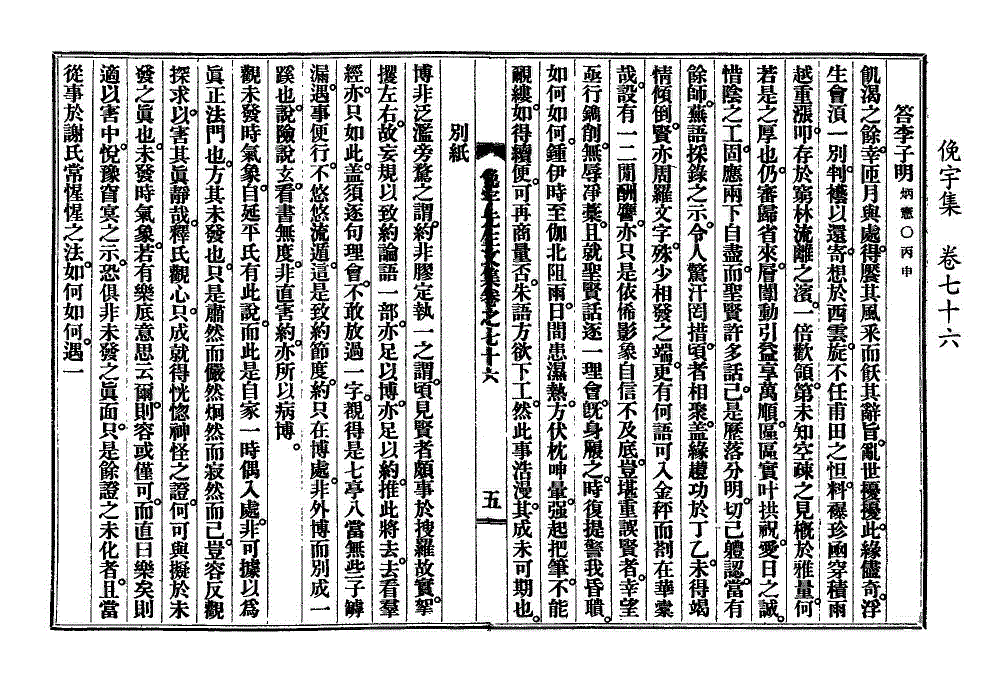 答李子明(炳宪○丙申)
答李子明(炳宪○丙申)饥渴之馀。幸匝月与处。得餍其风采而饫其辞旨。乱世扰扰。此缘尽奇。浮生会须一别。判襼以还。寄想于西云。旋不任甫田之怛。料襮珍函穿积雨越重涨。叩存于穷林流离之滨。一倍欢领。第未知空疏之见概于雅量。何若是之厚也。仍审归省来。层闱动引益享万顺。区区实叶拱祝。爱日之诚。惜阴之工。固应两下自尽。而圣贤许多话。已是历落分明。切己体认。当有馀师。芜语采录之示。令人惊汗罔措。顷者相聚。盖缘趱功于丁乙。未得竭情倾倒。贤亦周罗文字。殊少相发之端。更有何语可入金秤而劄在华橐哉。设有一二閒酬应。亦只是依俙影象自信不及底。岂堪重误贤者。幸望亟行镌削。无辱净藁。且就圣贤话逐一理会。既身履之。时复提警我昏聩。如何如何。钟伊时至伽北阻雨。日间患湿热。方伏枕呻晕。强起把笔。不能覼缕。如得续便。可再商量否。朱语方欲下工。然此事浩漫。其成未可期也。
别纸
博非泛滥旁骛之谓。约非胶定执一之谓。顷见贤者颇事于搜罗故实。挐攫左右。故妄规以致约论语一部。亦足以博。亦足以约。推此将去。去看群经。亦只如此。盖须逐句理会。不敢放过一字。睹得是七亭八当无些子罅漏。遇事便行。不悠悠流遁。这是致约节度。约只在博处。非外博而别成一蹊也。说险说玄。看书无度。非直害约。亦所以病博。
观未发时气象。自延平氏有此说。而此是自家一时偶入处。非可据以为真正法门也。方其未发也。只是肃然而俨然炯然而寂然而已。岂容反观探求。以害其真静哉。释氏观心。只成就得恍惚神怪之證。何可与拟于未发之真也。未发时气象。若有乐底意思云尔。则容或仅可。而直曰乐矣则适以害中。悦豫窅冥之示。恐俱非未发之真面。只是馀證之未化者。且当从事于谢氏常惺惺之法。如何如何。遇一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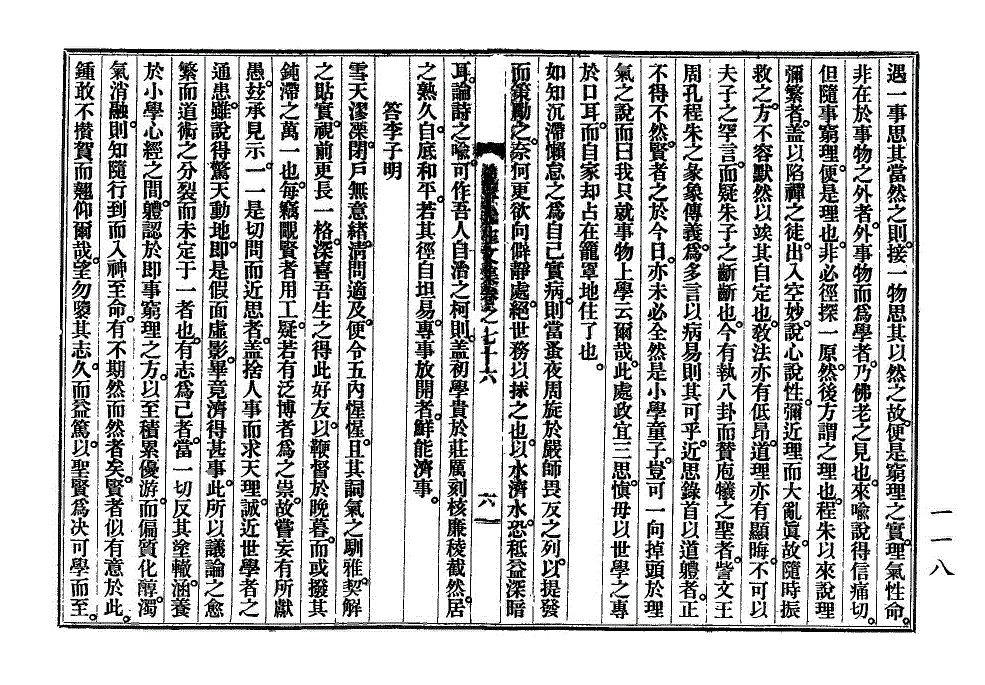 遇一事思其当然之则。接一物思其以然之故。便是穷理之实。理气性命。非在于事物之外者。外事物而为学者。乃佛老之见也。来喻说得信痛切。但随事穷理。便是理也。非必径探一原。然后方谓之理也。程朱以来说理弥繁者。盖以陷禅之徒。出入空妙。说心说性。弥近理而大乱真。故随时振救之。方不容默然以俟其自定也。教法亦有低昂。道理亦有显晦。不可以夫子之罕言。而疑朱子之龂龂也。今有执八卦而赞庖牺之圣者。訾文王周孔程朱之彖象传义。为多言以病易则其可乎。近思录首以道体者。正不得不然。贤者之于今日。亦未必全然是小学童子。岂可一向掉头于理气之说而曰我只就事物上学云尔哉。此处政宜三思。慎毋以世学之专于口耳。而自家却占在笼罩地住了也。
遇一事思其当然之则。接一物思其以然之故。便是穷理之实。理气性命。非在于事物之外者。外事物而为学者。乃佛老之见也。来喻说得信痛切。但随事穷理。便是理也。非必径探一原。然后方谓之理也。程朱以来说理弥繁者。盖以陷禅之徒。出入空妙。说心说性。弥近理而大乱真。故随时振救之。方不容默然以俟其自定也。教法亦有低昂。道理亦有显晦。不可以夫子之罕言。而疑朱子之龂龂也。今有执八卦而赞庖牺之圣者。訾文王周孔程朱之彖象传义。为多言以病易则其可乎。近思录首以道体者。正不得不然。贤者之于今日。亦未必全然是小学童子。岂可一向掉头于理气之说而曰我只就事物上学云尔哉。此处政宜三思。慎毋以世学之专于口耳。而自家却占在笼罩地住了也。如知沉滞懒怠之为自己实病。则当蚤夜周旋于严师畏友之列。以提发而策励之。奈何更欲向僻静处。绝世务以救之也。以水济水。恐秪益深暗耳。论诗之喻。可作吾人自治之柯则。盖初学贵于庄厉刻核廉棱截然。居之熟久。自底和平。若其径自坦易。专事放开者。鲜能济事。
答李子明
雪天漻凓。闭户无意绪。清问适及。便令五内惺惺。且其词气之驯雅。契解之贴实。视前更长一格。深喜吾生之得此好友。以鞭督于晚暮。而或拨其钝滞之万一也。每窃覸贤者用工。疑若有泛博者为之祟。故尝妄有所献愚。玆承见示。一一是切问而近思者。盖舍人事而求天理。诚近世学者之通患。虽说得惊天动地。即是假面虚影。毕竟济得甚事。此所以议论之愈繁而道术之分裂而未定于一者也。有志为己者。当一切反其涂辙。涵养于小学心经之间。体认于即事穷理之方。以至积累优游。而偏质化醇。浊气消融。则知随行到而入神至命。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贤者似有意于此。钟敢不攒贺而翘仰尔哉。望勿隳其志。久而益笃。以圣贤为决可学而至。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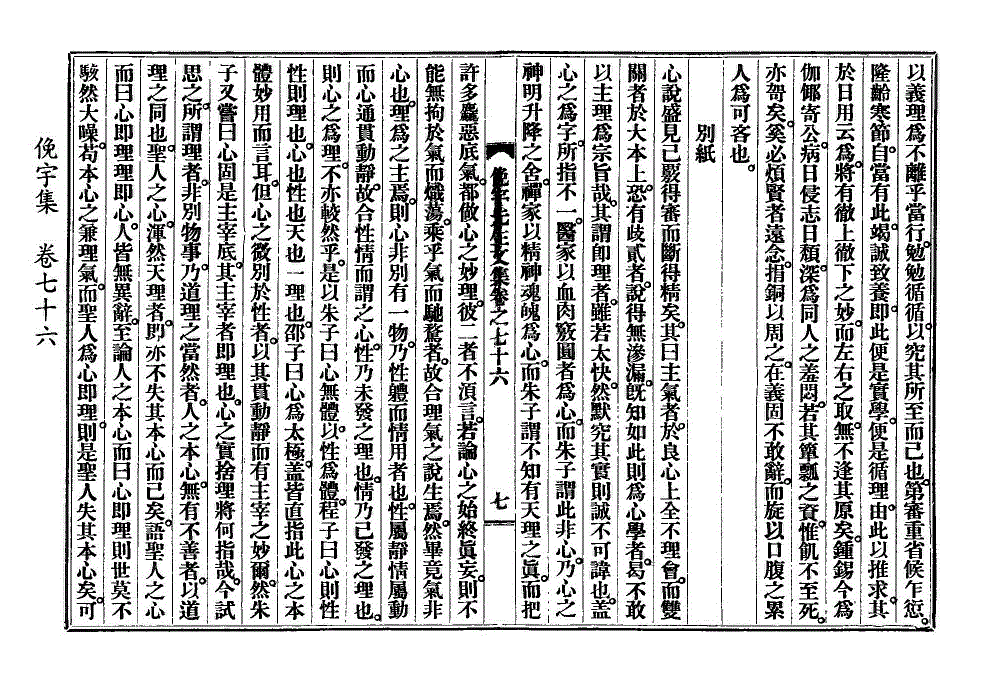 以义理为不离乎当行。勉勉循循。以究其所至而已也。第审重省候乍愆。隆龄寒节。自当有此。竭诚致养。即此便是实学。便是循理。由此以推求。其于日用云为。将有彻上彻下之妙。而左右之取。无不逢其原矣。钟锡今为伽倻寄公。病日侵志日颓。深为同人之羞闷。若其箪瓢之资。惟饥不至死。亦哿矣。奚必烦贤者远念。捐铜以周之。在义固不敢辞。而旋以口腹之累人为可吝也。
以义理为不离乎当行。勉勉循循。以究其所至而已也。第审重省候乍愆。隆龄寒节。自当有此。竭诚致养。即此便是实学。便是循理。由此以推求。其于日用云为。将有彻上彻下之妙。而左右之取。无不逢其原矣。钟锡今为伽倻寄公。病日侵志日颓。深为同人之羞闷。若其箪瓢之资。惟饥不至死。亦哿矣。奚必烦贤者远念。捐铜以周之。在义固不敢辞。而旋以口腹之累人为可吝也。别纸
心说盛见已覈得审而断得精矣。其曰主气者。于良心上全不理会。而双关者于大本上。恐有歧贰者。说得无渗漏。既知如此则为心学者。曷不敢以主理为宗旨哉。其谓即理者。虽若太快。然默究其实则诚不可讳也。盖心之为字。所指不一。医家以血肉窍圆者为心。而朱子谓此非心。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禅家以精神魂魄为心。而朱子谓不知有天理之真。而把许多粗恶底气。都做心之妙理。彼二者不须言。若论心之始终真妄。则不能无拘于气而炽荡。乘乎气而驰骛者。故合理气之说生焉。然毕竟气非心也。理为之主焉。则心非别有一物。乃性体而情用者也。性属静情属动而心通贯动静。故合性情而谓之心。性乃未发之理也。情乃已发之理也。则心之为理。不亦较然乎。是以朱子曰心无体。以性为体。程子曰心则性性则理也。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邵子曰心为太极。盖皆直指此心之本体妙用而言耳。但心之微别于性者。以其贯动静而有主宰之妙尔。然朱子又尝曰心固是主宰底。其主宰者即理也。心之实舍理将何指哉。今试思之。所谓理者。非别物事。乃道理之当然者。人之本心。无有不善者。以道理之同也。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者。即亦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语圣人之心而曰心即理理即心。人皆无异辞。至论人之本心而曰心即理则世莫不骇然大噪。苟本心之兼理气。而圣人为心即理。则是圣人失其本心矣。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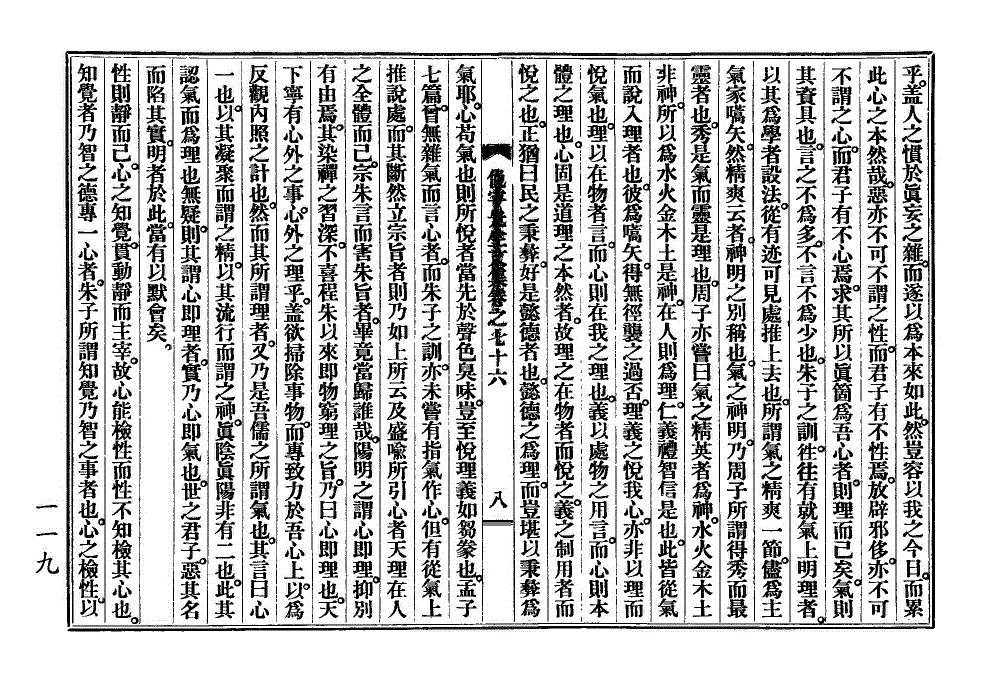 乎。盖人之惯于真妄之杂。而遂以为本来如此。然岂容以我之今日。而累此心之本然哉。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而君子有不性焉。放辟邪侈。亦不可不谓之心。而君子有不心焉。求其所以真个为吾心者。则理而已矣。气则其资具也。言之不为多。不言不为少也。朱子之训。往往有就气上明理者。以其为学者设法。从有迹可见处推上去也。所谓气之精爽一节。尽为主气家嚆矢。然精爽云者。神明之别称也。气之神明。乃周子所谓得秀而最灵者也。秀是气而灵是理也。朱子亦尝曰气之精英者为神。水火金木土非神。所以为水火金木土是神。在人则为理。仁义礼智信是也。此皆从气而说入理者也。彼为嚆矢。得无径袭之过否。理义之悦我心。亦非以理而悦气也。理以在物者言。而心则在我之理也。义以处物之用言。而心则本体之理也。心固是道理之本然者。故理之在物者而悦之。义之制用者而悦之也。正犹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懿德之为理。而岂堪以秉彝为气耶。心苟气也则所悦者当先于声色臭味。岂至悦理义如刍豢也。孟子七篇。曾无杂气而言心者。而朱子之训。亦未尝有指气作心。但有从气上推说处。而其断然立宗旨者则乃如上所云及盛喻所引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而已。宗朱言而害朱旨者。毕竟当归谁哉。阳明之谓心即理。抑别有由焉。其染禅之习深。不喜程朱以来即物穷理之旨。乃曰心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盖欲扫除事物。而专致力于吾心上。以为反观内照之计也。然而其所谓理者。又乃是吾儒之所谓气也。其言曰心一也。以其凝聚而谓之精。以其流行而谓之神。真阴真阳非有二也。此其认气而为理也无疑。则其谓心即理者。实乃心即气也。世之君子。恶其名而陷其实。明者于此。当有以默会矣。
乎。盖人之惯于真妄之杂。而遂以为本来如此。然岂容以我之今日。而累此心之本然哉。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而君子有不性焉。放辟邪侈。亦不可不谓之心。而君子有不心焉。求其所以真个为吾心者。则理而已矣。气则其资具也。言之不为多。不言不为少也。朱子之训。往往有就气上明理者。以其为学者设法。从有迹可见处推上去也。所谓气之精爽一节。尽为主气家嚆矢。然精爽云者。神明之别称也。气之神明。乃周子所谓得秀而最灵者也。秀是气而灵是理也。朱子亦尝曰气之精英者为神。水火金木土非神。所以为水火金木土是神。在人则为理。仁义礼智信是也。此皆从气而说入理者也。彼为嚆矢。得无径袭之过否。理义之悦我心。亦非以理而悦气也。理以在物者言。而心则在我之理也。义以处物之用言。而心则本体之理也。心固是道理之本然者。故理之在物者而悦之。义之制用者而悦之也。正犹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懿德之为理。而岂堪以秉彝为气耶。心苟气也则所悦者当先于声色臭味。岂至悦理义如刍豢也。孟子七篇。曾无杂气而言心者。而朱子之训。亦未尝有指气作心。但有从气上推说处。而其断然立宗旨者则乃如上所云及盛喻所引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而已。宗朱言而害朱旨者。毕竟当归谁哉。阳明之谓心即理。抑别有由焉。其染禅之习深。不喜程朱以来即物穷理之旨。乃曰心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盖欲扫除事物。而专致力于吾心上。以为反观内照之计也。然而其所谓理者。又乃是吾儒之所谓气也。其言曰心一也。以其凝聚而谓之精。以其流行而谓之神。真阴真阳非有二也。此其认气而为理也无疑。则其谓心即理者。实乃心即气也。世之君子。恶其名而陷其实。明者于此。当有以默会矣。性则静而已。心之知觉。贯动静而主宰。故心能检性而性不知检其心也。知觉者乃智之德专一心者。朱子所谓知觉乃智之事者也。心之检性。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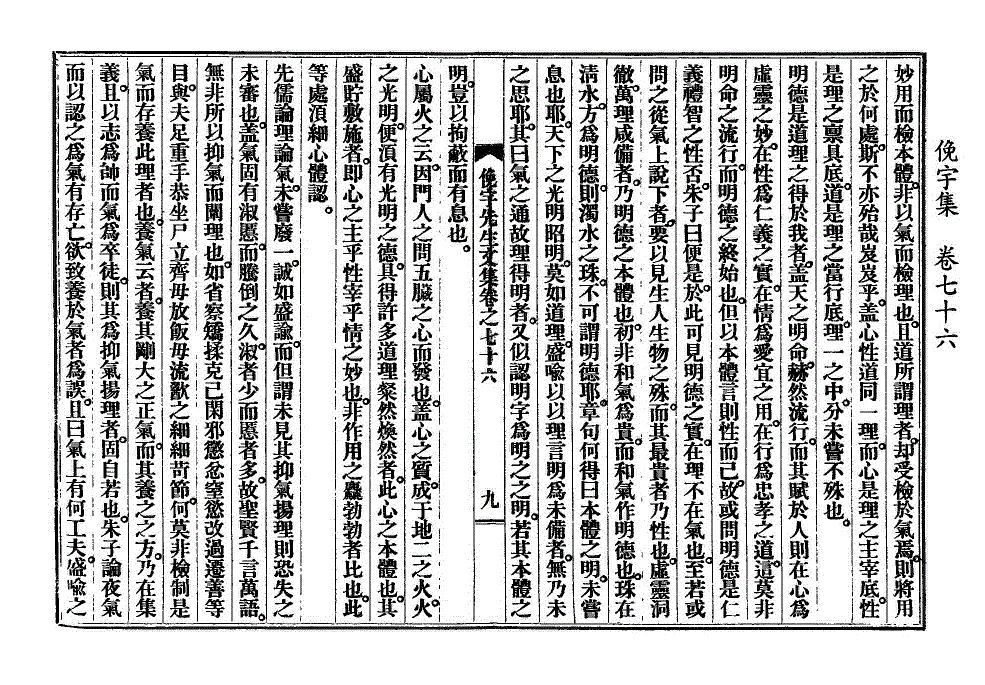 妙用而检本体。非以气而检理也。且道所谓理者。却受检于气焉。则将用之于何处。斯不亦殆哉岌岌乎。盖心性道同一理。而心是理之主宰底。性是理之禀具底。道是理之当行底。理一之中。分未尝不殊也。
妙用而检本体。非以气而检理也。且道所谓理者。却受检于气焉。则将用之于何处。斯不亦殆哉岌岌乎。盖心性道同一理。而心是理之主宰底。性是理之禀具底。道是理之当行底。理一之中。分未尝不殊也。明德是道理之得于我者。盖天之明命。赫然流行。而其赋于人则在心为虚灵之妙。在性为仁义之实。在情为爱宜之用。在行为忠孝之道。这莫非明命之流行。而明德之终始也。但以本体言则性而已。故或问明德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朱子曰便是。于此可见明德之实。在理不在气也。至若或问之从气上说下者。要以见生人生物之殊。而其最贵者乃性也。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者。乃明德之本体也。初非和气为贵。而和气作明德也。珠在清水。方为明德。则浊水之珠。不可谓明德耶。章句何得曰本体之明。未尝息也耶。天下之光明昭明。莫如道理。盛喻以以理言明为未备者。无乃未之思耶。其曰气之通故理得明者。又似认明字为明之之明。若其本体之明。岂以拘蔽而有息也。
心属火之云。因门人之问五脏之心而发也。盖心之质。成于地二之火。火之光明。便须有光明之德。具得许多道理粲然焕然者。此心之本体也。其盛贮敷施者。即心之主乎性宰乎情之妙也。非作用之粗勃勃者比也。此等处须细心体认。
先儒论理论气。未尝废一。诚如盛谕。而但谓未见其抑气扬理则恐失之未审也。盖气固有淑慝。而腾倒之久。淑者少而慝者多。故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所以抑气而阐理也。如省察矫揉克己闲邪惩忿窒欲改过迁善等目。与夫足重手恭坐尸立齐毋放饭毋流歠之细细苛节。何莫非检制是气而存养此理者也。养气云者。养其刚大之正气。而其养之之方。乃在集义。且以志为帅而气为卒徒。则其为抑气扬理者。固自若也。朱子论夜气而以认之为气有存亡。欲致养于气者为误。且曰气上有何工夫。盛喻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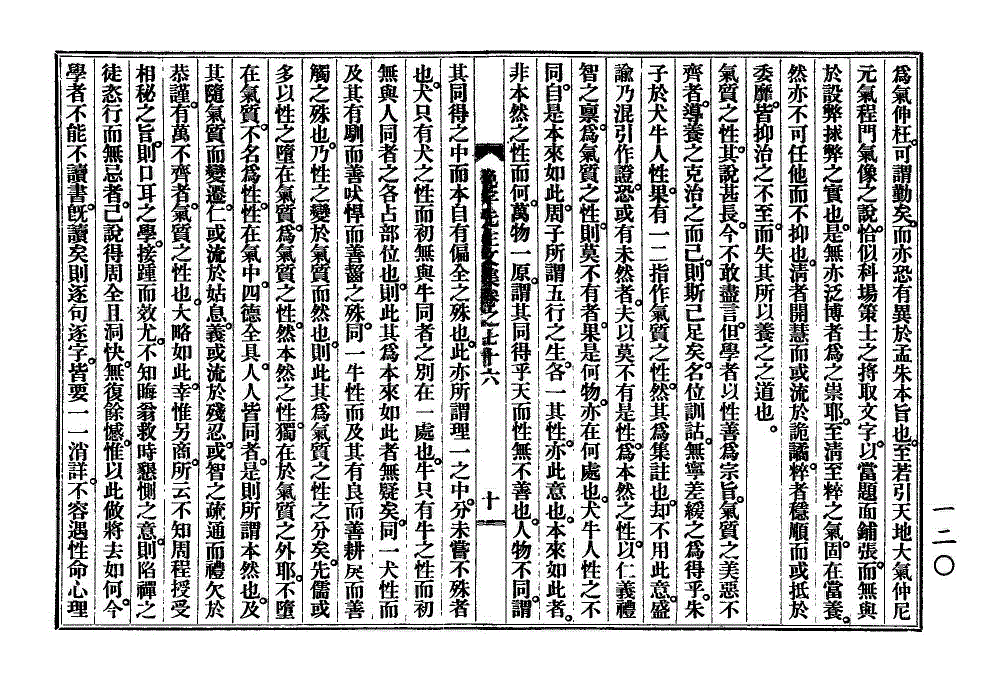 为气伸枉。可谓勤矣。而亦恐有异于孟朱本旨也。至若引天地大气仲尼元气程门气像之说。恰似科场策士之捋取文字。以当题面铺张。而无与于设弊救弊之实也。是无亦泛博者为之祟耶。至清至粹之气。固在当养。然亦不可任他而不抑也。清者开慧而或流于诡谲。粹者稳顺而或抵于委靡。皆抑治之不至。而失其所以养之之道也。
为气伸枉。可谓勤矣。而亦恐有异于孟朱本旨也。至若引天地大气仲尼元气程门气像之说。恰似科场策士之捋取文字。以当题面铺张。而无与于设弊救弊之实也。是无亦泛博者为之祟耶。至清至粹之气。固在当养。然亦不可任他而不抑也。清者开慧而或流于诡谲。粹者稳顺而或抵于委靡。皆抑治之不至。而失其所以养之之道也。气质之性。其说甚长。今不敢尽言。但学者以性善为宗旨。气质之美恶不齐者。导养之克治之而已。则斯已足矣。名位训诂。无宁差缓之为得乎。朱子于犬牛人性。果有一二指作气质之性。然其为集注也。却不用此意。盛谕乃混引作證。恐或有未然者。夫以莫不有是性。为本然之性。以仁义礼智之禀。为气质之性。则莫不有者。果是何物。亦在何处也。犬牛人性之不同。自是本来如此。周子所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亦此意也。本来如此者。非本然之性而何。万物一原。谓其同得乎天而性无不善也。人物不同。谓其同得之中而本自有偏全之殊也。此亦所谓理一之中。分未尝不殊者也。犬只有犬之性而初无与牛同者之别在一处也。牛只有牛之性而初无与人同者之各占部位也。则此其为本来如此者无疑矣。同一犬性而及其有驯而善吠悍而善齧之殊。同一牛性而及其有良而善耕戾而善触之殊也。乃性之变于气质而然也。则此其为气质之性之分矣。先儒或多以性之堕在气质。为气质之性。然本然之性。独在于气质之外耶。不堕在气质。不名为性。性在气中。四德全具。人人皆同者。是则所谓本然也。及其随气质而变迁。仁或流于姑息。义或流于残忍。或智之疏通而礼欠于恭谨。有万不齐者。气质之性也。大略如此。幸惟另商。所云不知周程授受相秘之旨。则日耳之学。接踵而效尤。不知晦翁救时恳恻之意。则陷禅之徒恣行而无忌者。已说得周全且洞快。无复馀憾。惟以此做将去如何。今学者不能不读书。既读矣则逐句逐字。皆要一一消详。不容遇性命心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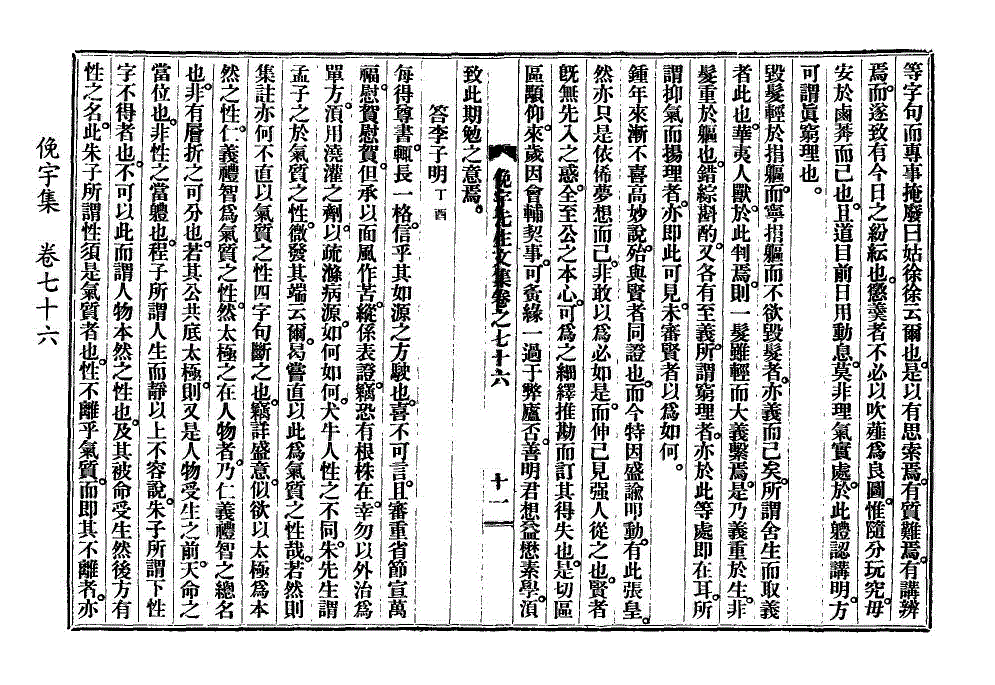 等字句而专事掩废曰姑徐徐云尔也。是以有思索焉。有质难焉。有讲辨焉。而遂致有今日之纷纭也。惩羹者不必以吹薤为良图。惟随分玩究。毋安于卤莽而已也。且道目前日用动息。莫非理气实处。于此体认讲明。方可谓真穷理也。
等字句而专事掩废曰姑徐徐云尔也。是以有思索焉。有质难焉。有讲辨焉。而遂致有今日之纷纭也。惩羹者不必以吹薤为良图。惟随分玩究。毋安于卤莽而已也。且道目前日用动息。莫非理气实处。于此体认讲明。方可谓真穷理也。毁发轻于捐躯。而宁捐躯而不欲毁发者。亦义而已矣。所谓舍生而取义者此也。华夷人兽。于此判焉。则一发虽轻而大义系焉。是乃义重于生。非发重于躯也。错综斟酌。又各有至义。所谓穷理者。亦于此等处即在耳。所谓抑气而扬理者。亦即此可见。未审贤者以为如何。
钟年来渐不喜高妙说。殆与贤者同證也。而今特因盛谕叩动。有此张皇。然亦只是依俙梦想而已。非敢以为必如是。而伸己见强人从之也。贤者既无先入之惑。全至公之本心。可为之细绎推勘而订其得失也。是切区区颙仰。来岁因会辅契事。可夤缘一过于弊庐否。善明君想益懋素学。须致此期勉之意焉。
答李子明(丁酉)
每得尊书。辄长一格。信乎其如源之方驶也。喜不可言。且审重省节宣万福。慰贺慰贺。但承以面风作苦。纵系表證。窃恐有根株在。幸勿以外治为单方。须用浇灌之剂。以疏涤病源。如何如何。犬牛人性之不同。朱先生谓孟子之于气质之性。微发其端云尔。曷尝直以此为气质之性哉。若然则集注亦何不直以气质之性四字句断之也。窃详盛意。似欲以太极为本然之性。仁义礼智为气质之性。然太极之在人物者。乃仁义礼智之总名也。非有层折之可分也。若其公共底太极。则又是人物受生之前。天命之当位也。非性之当体也。程子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朱子所谓下性字不得者也。不可以此而谓人物本然之性也。及其被命受生然后方有性之名。此朱子所谓性须是气质者也。性不离乎气质。而即其不离者。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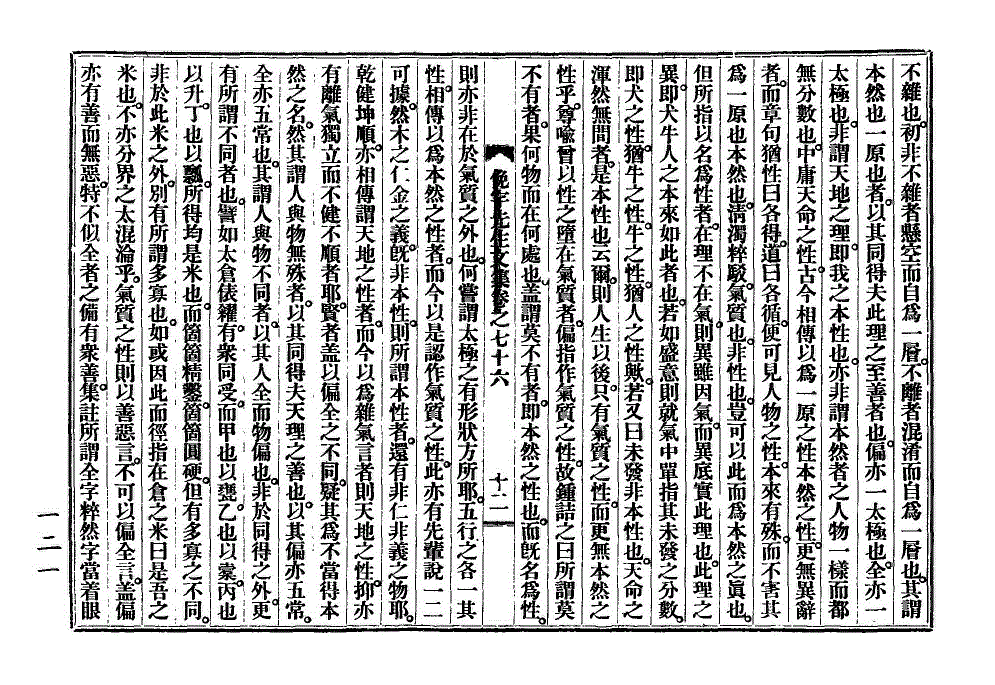 不杂也。初非不杂者悬空而自为一层。不离者混淆而自为一层也。其谓本然也一原也者。以其同得夫此理之至善者也。偏亦一太极也。全亦一太极也。非谓天地之理。即我之本性也。亦非谓本然者之人物一样而都无分数也。中庸天命之性。古今相传以为一原之性本然之性。更无异辞者。而章句犹性曰各得。道曰各循。便可见人物之性。本来有殊。而不害其为一原也本然也。清浊粹驳。气质也。非性也。岂可以此而为本然之真也。但所指以名为性者。在理不在气。则异虽因气。而异底实此理也。此理之异。即犬牛人之本来如此者也。若如盛意则就气中单指其未发之分数。即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若又曰未发非本性也。天命之浑然无间者。是本性也云尔。则人生以后。只有气质之性。而更无本然之性乎。尊喻曾以性之堕在气质者。偏指作气质之性。故钟诘之曰所谓莫不有者。果何物而在何处也。盖谓莫不有者。即本然之性也。而既名为性。则亦非在于气质之外也。何尝谓太极之有形状方所耶。五行之各一其性。相传以为本然之性者。而今以是认作气质之性。此亦有先辈说一二可据。然木之仁金之义。既非本性。则所谓本性者。还有非仁非义之物耶。乾健坤顺。亦相传谓天地之性者。而今以为杂气言者则天地之性。抑亦有离气独立而不健不顺者耶。贤者盖以偏全之不同。疑其为不当得本然之名。然其谓人与物无殊者。以其同得夫天理之善也。以其偏亦五常。全亦五常也。其谓人与物不同者。以其人全而物偏也。非于同得之外。更有所谓不同者也。譬如太仓俵籴(一作粜)。有众同受。而甲也以瓮。乙也以橐。丙也以升。丁也以瓢。所得均是米也。而个个精凿。个个圆硬。但有多寡之不同。非于此米之外。别有所谓多寡也。如或因此而径指在仓之米曰是吾之米也。不亦分界之太混沦乎。气质之性则以善恶言。不可以偏全言。盖偏亦有善而无恶。特不似全者之备有众善。集注所谓全字粹然字当着眼
不杂也。初非不杂者悬空而自为一层。不离者混淆而自为一层也。其谓本然也一原也者。以其同得夫此理之至善者也。偏亦一太极也。全亦一太极也。非谓天地之理。即我之本性也。亦非谓本然者之人物一样而都无分数也。中庸天命之性。古今相传以为一原之性本然之性。更无异辞者。而章句犹性曰各得。道曰各循。便可见人物之性。本来有殊。而不害其为一原也本然也。清浊粹驳。气质也。非性也。岂可以此而为本然之真也。但所指以名为性者。在理不在气。则异虽因气。而异底实此理也。此理之异。即犬牛人之本来如此者也。若如盛意则就气中单指其未发之分数。即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若又曰未发非本性也。天命之浑然无间者。是本性也云尔。则人生以后。只有气质之性。而更无本然之性乎。尊喻曾以性之堕在气质者。偏指作气质之性。故钟诘之曰所谓莫不有者。果何物而在何处也。盖谓莫不有者。即本然之性也。而既名为性。则亦非在于气质之外也。何尝谓太极之有形状方所耶。五行之各一其性。相传以为本然之性者。而今以是认作气质之性。此亦有先辈说一二可据。然木之仁金之义。既非本性。则所谓本性者。还有非仁非义之物耶。乾健坤顺。亦相传谓天地之性者。而今以为杂气言者则天地之性。抑亦有离气独立而不健不顺者耶。贤者盖以偏全之不同。疑其为不当得本然之名。然其谓人与物无殊者。以其同得夫天理之善也。以其偏亦五常。全亦五常也。其谓人与物不同者。以其人全而物偏也。非于同得之外。更有所谓不同者也。譬如太仓俵籴(一作粜)。有众同受。而甲也以瓮。乙也以橐。丙也以升。丁也以瓢。所得均是米也。而个个精凿。个个圆硬。但有多寡之不同。非于此米之外。别有所谓多寡也。如或因此而径指在仓之米曰是吾之米也。不亦分界之太混沦乎。气质之性则以善恶言。不可以偏全言。盖偏亦有善而无恶。特不似全者之备有众善。集注所谓全字粹然字当着眼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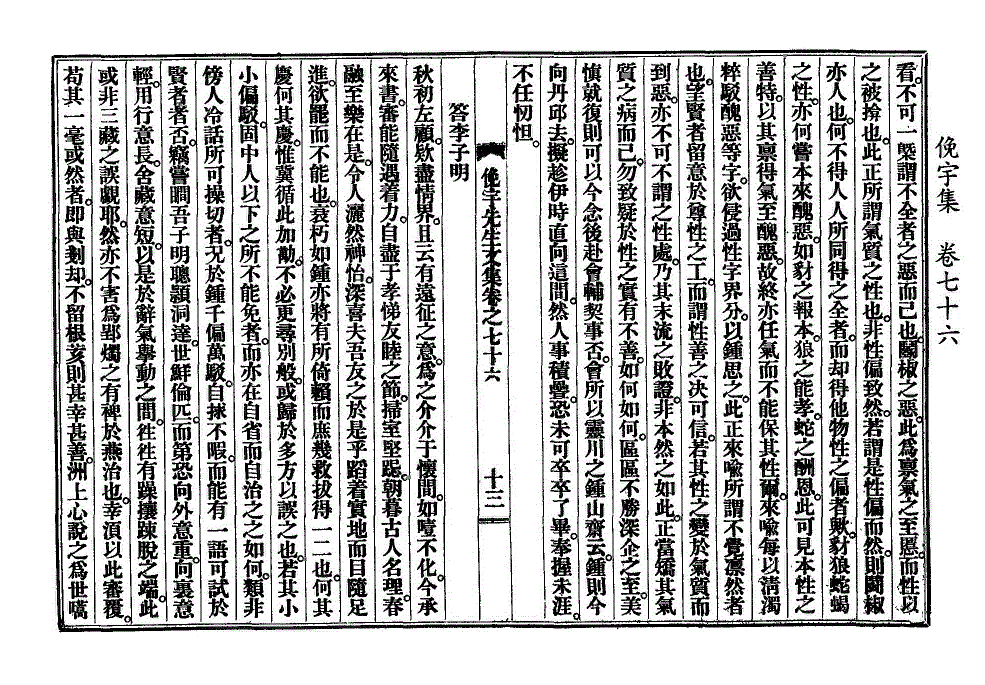 看。不可一槩谓不全者之恶而已也。斗椒之恶。此为禀气之至慝。而性以之被掩也。此正所谓气质之性也。非性偏致然。若谓是性偏而然。则斗椒亦人也。何不得人人所同得之全者。而却得他物性之偏者欤。豺狼蛇蝎之性。亦何尝本来丑恶。如豺之报本。狼之能孝。蛇之酬恩。此可见本性之善特。以其禀得气至丑恶。故终亦任气而不能保其性尔。来喻每以清浊粹驳丑恶等字。欲侵过性字界分。以钟思之。此正来喻所谓不觉凛然者也。望贤者留意于尊性之工。而谓性善之决可信。若其性之变于气质而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处。乃其末流之败證。非本然之如此。正当矫其气质之病而已。勿致疑于性之实有不善。如何如何。区区不胜深企之至。美慎就复则可以今念后赴会辅契事否。会所以灵川之钟山斋云。钟则今向丹邱去。拟趁伊时直向这间。然人事积叠。恐未可卒卒了毕。奉握未涯。不任忉怛。
看。不可一槩谓不全者之恶而已也。斗椒之恶。此为禀气之至慝。而性以之被掩也。此正所谓气质之性也。非性偏致然。若谓是性偏而然。则斗椒亦人也。何不得人人所同得之全者。而却得他物性之偏者欤。豺狼蛇蝎之性。亦何尝本来丑恶。如豺之报本。狼之能孝。蛇之酬恩。此可见本性之善特。以其禀得气至丑恶。故终亦任气而不能保其性尔。来喻每以清浊粹驳丑恶等字。欲侵过性字界分。以钟思之。此正来喻所谓不觉凛然者也。望贤者留意于尊性之工。而谓性善之决可信。若其性之变于气质而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处。乃其末流之败證。非本然之如此。正当矫其气质之病而已。勿致疑于性之实有不善。如何如何。区区不胜深企之至。美慎就复则可以今念后赴会辅契事否。会所以灵川之钟山斋云。钟则今向丹邱去。拟趁伊时直向这间。然人事积叠。恐未可卒卒了毕。奉握未涯。不任忉怛。答李子明
秋初左顾。款尽情界。且云有远征之意。为之介介于怀间。如噎不化。今承来书。审能随遇着力。自尽于孝悌友睦之节。扫室坚跽。朝暮古人名理。春融至乐在是。令人洒然神怡。深喜夫吾友之于是乎蹈着实地而目随足进。欲罢而不能也。衰朽如钟亦将有所倚赖而庶几救拔得一二也。何其庆何其庆。惟冀循此加劢。不必更寻别般。或归于多方以误之也。若其小小偏驳。固中人以下之所不能免者。而亦在自省而自治之之如何。类非傍人冷话所可操切者。况于钟千偏万驳。自救不暇。而能有一语可试于贤者者否。窃尝瞷吾子明聪颖洞达。世鲜伦匹。而第恐向外意重。向里意轻。用行意长。舍藏意短。以是于辞气举动之间。往往有躁攘疏脱之端。此或非三藏之误觑耶。然亦不害为郢烛之有裨于燕治也。幸须以此审覆。苟其一毫或然者。即与刬却。不留根荄则甚幸甚善。洲上心说之为世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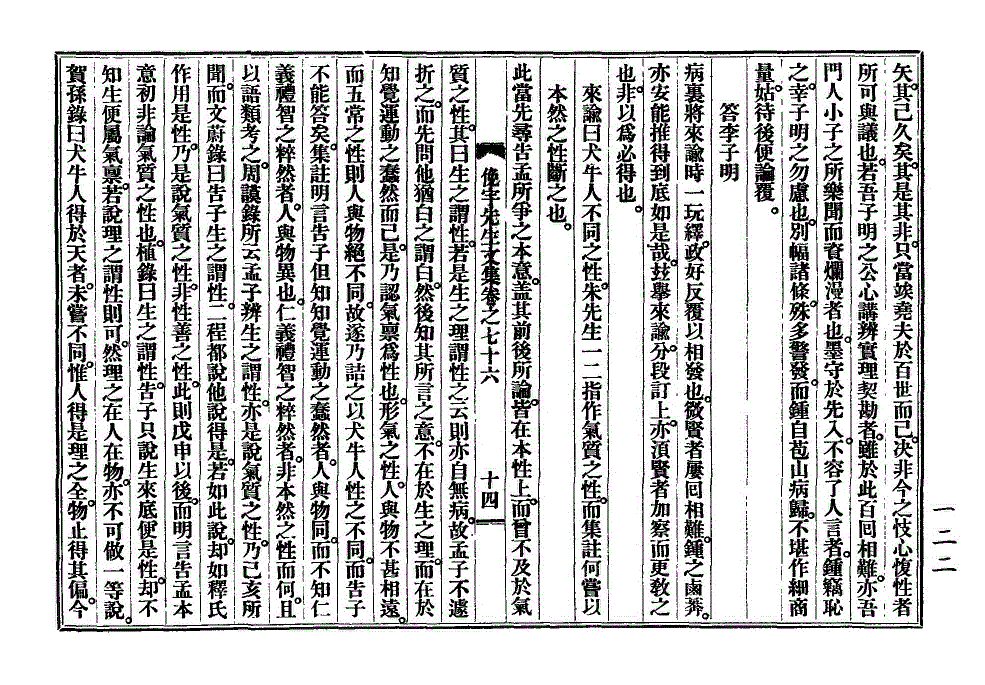 矢。其已久矣。其是其非。只当俟尧夫于百世而已。决非今之忮心愎性者所可与议也。若吾子明之公心讲辨实理契勘者。虽于此百回相难。亦吾门人小子之所乐闻而资烂漫者也。墨守于先入。不容了人言者。钟窃耻之。幸子明之勿虑也。别幅诸条。殊多警发。而钟自苞山病归。不堪作细商量。姑待后便论覆。
矢。其已久矣。其是其非。只当俟尧夫于百世而已。决非今之忮心愎性者所可与议也。若吾子明之公心讲辨实理契勘者。虽于此百回相难。亦吾门人小子之所乐闻而资烂漫者也。墨守于先入。不容了人言者。钟窃耻之。幸子明之勿虑也。别幅诸条。殊多警发。而钟自苞山病归。不堪作细商量。姑待后便论覆。答李子明
病里将来谕时一玩绎。政好反覆以相发也。微贤者屡回相难。钟之卤莽。亦安能推得到底如是哉。玆举来谕。分段订上。亦须贤者加察而更教之也。非以为必得也。
来谕曰犬牛人不同之性。朱先生一二指作气质之性。而集注何尝以本然之性断之也。
此当先寻告孟所争之本意。盖其前后所论。皆在本性上。而曾不及于气质之性。其曰生之谓性。若是生之理谓性之云则亦自无病。故孟子不遽折之。而先问他犹白之谓白。然后知其所言之意。不在于生之理。而在于知觉运动之蠢然而已。是乃认气禀为性也。形气之性。人与物不甚相远。而五常之性则人与物绝不同。故遂乃诘之以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告子不能答矣。集注明言告子但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仁义礼智之粹然者。非本然之性而何。且以语类考之。周谟录所云孟子辨生之谓性。亦是说气质之性。乃己亥所闻。而文蔚录曰告子生之谓性。二程都说他说得是。若如此说。却如释氏作用是性。乃是说气质之性。非性善之性。此则戊申以后。而明言告孟本意初非论气质之性也。植录曰生之谓性。告子只说生来底便是性。却不知生便属气禀。若说理之谓性则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说。贺孙录曰犬牛人得于天者。未尝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物止得其偏。今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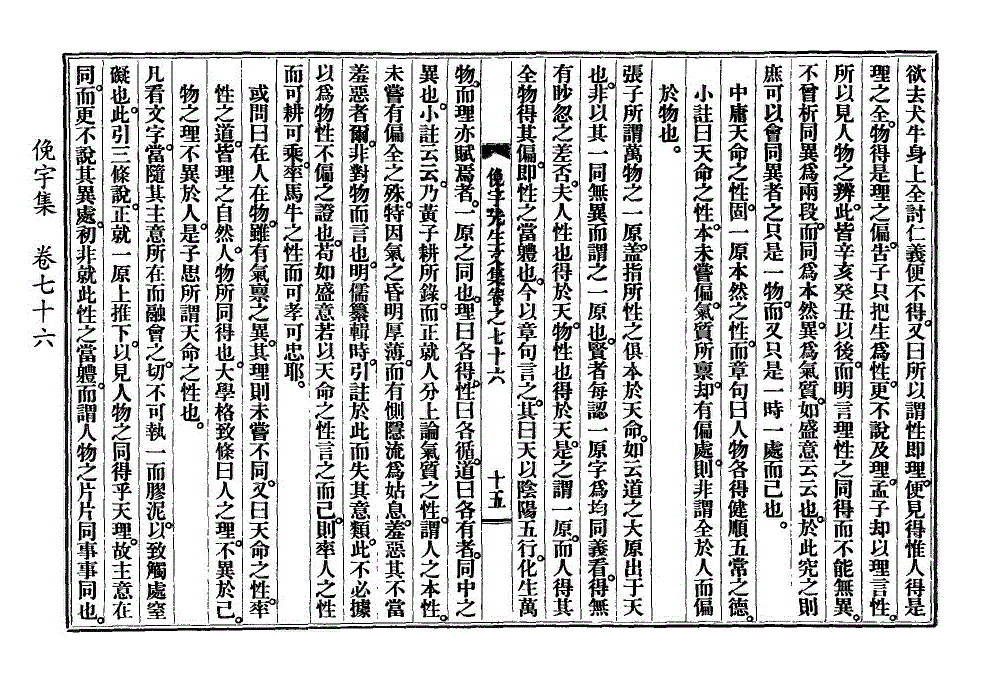 欲去犬牛身上全讨仁义便不得。又曰所以谓性即理。便见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只把生为性。更不说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见人物之辨。此皆辛亥癸丑以后。而明言理性之同得而不能无异。不曾析同异为两段。而同为本然。异为气质。如盛意云云也。于此究之则庶可以会同异者之只是一物。而又只是一时一处而已也。
欲去犬牛身上全讨仁义便不得。又曰所以谓性即理。便见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只把生为性。更不说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见人物之辨。此皆辛亥癸丑以后。而明言理性之同得而不能无异。不曾析同异为两段。而同为本然。异为气质。如盛意云云也。于此究之则庶可以会同异者之只是一物。而又只是一时一处而已也。中庸天命之性。固一原本然之性。而章句曰人物各得健顺五常之德。小注曰天命之性。本未尝偏。气质所禀。却有偏处。则非谓全于人而偏于物也。
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盖指所性之俱本于天命。如云道之大原出于天也。非以其一同无异而谓之一原也。贤者每认一原字为均同义看。得无有眇忽之差否。夫人性也得于天。物性也得于天。是之谓一原。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即性之当体也。今以章句言之。其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而理亦赋焉者。一原之同也。理曰各得。性曰各循。道曰各有者。同中之异也。小注云云。乃黄子耕所录。而正就人分上论气质之性。谓人之本性。未尝有偏全之殊。特因气之昏明厚薄。而有恻隐流为姑息。羞恶其不当羞恶者尔。非对物而言也。明儒纂辑时。引注于此而失其意类。此不必据以为物性不偏之證也。苟如盛意若以天命之性言之而已。则率人之性而可耕可乘。率马牛之性而可孝可忠耶。
或问曰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异。其理则未尝不同。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人物所同得也。大学格致条曰人之理。不异于己。物之理不异于人。是子思所谓天命之性也。
凡看文字。当随其主意所在而融会之。切不可执一而胶泥。以致触处窒碍也。此引三条说。正就一原上推下。以见人物之同得乎天理。故主意在同。而更不说其异处。初非就此性之当体。而谓人物之片片同事事同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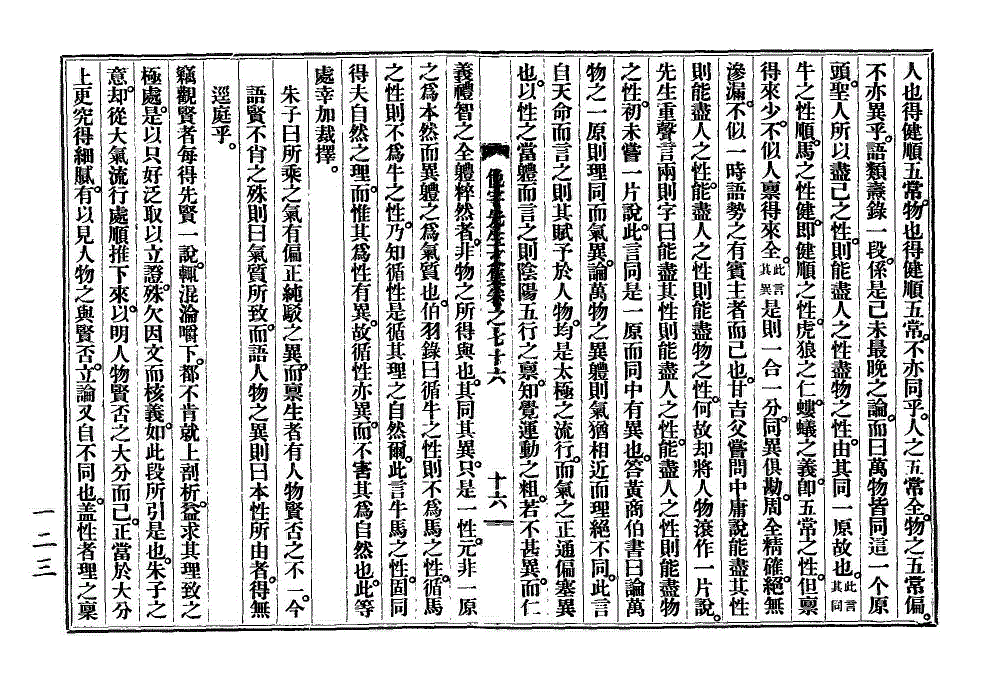 人也得健顺五常。物也得健顺五常。不亦同乎。人之五常全。物之五常偏。不亦异乎。语类焘录一段。系是己未最晚之论。而曰万物皆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此言其同)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此言其异)是则一合一分。同异俱勘。周全精确。绝无渗漏。不似一时语势之有宾主者而已也。甘吉父尝问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何故却将人物滚作一片说。先生重声言两则字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初未尝一片说。此言同是一原而同中有异也。答黄商伯书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言自天命而言之则其赋予于人物。均是太极之流行。而气之正通偏塞异也。以性之当体而言之则阴阳五行之禀。知觉运动之粗。若不甚异而仁义礼智之全体粹然者。非物之所得与也。其同其异。只是一性。元非一原之为本然而异体之为气质也。伯羽录曰循牛之性则不为马之性。循马之性则不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尔。此言牛马之性。固同得夫自然之理。而惟其为性有异。故循性亦异。而不害其为自然也。此等处幸加裁择。
人也得健顺五常。物也得健顺五常。不亦同乎。人之五常全。物之五常偏。不亦异乎。语类焘录一段。系是己未最晚之论。而曰万物皆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此言其同)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此言其异)是则一合一分。同异俱勘。周全精确。绝无渗漏。不似一时语势之有宾主者而已也。甘吉父尝问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何故却将人物滚作一片说。先生重声言两则字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初未尝一片说。此言同是一原而同中有异也。答黄商伯书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言自天命而言之则其赋予于人物。均是太极之流行。而气之正通偏塞异也。以性之当体而言之则阴阳五行之禀。知觉运动之粗。若不甚异而仁义礼智之全体粹然者。非物之所得与也。其同其异。只是一性。元非一原之为本然而异体之为气质也。伯羽录曰循牛之性则不为马之性。循马之性则不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尔。此言牛马之性。固同得夫自然之理。而惟其为性有异。故循性亦异。而不害其为自然也。此等处幸加裁择。朱子曰所乘之气有偏正纯驳之异。而禀生者有人物贤否之不一。今语贤不肖之殊则曰气质所致。而语人物之异则曰本性所由者。得无径庭乎。
窃观贤者每得先贤一说。辄混沦嚼下。都不肯就上剖析。益求其理致之极处。是以只好泛取以立證。殊欠因文而核义。如此段所引是也。朱子之意。却从大气流行处顺推下来。以明人物贤否之大分而已。正当于大分上更究得细腻。有以见人物之与贤否。立论又自不同也。盖性者理之禀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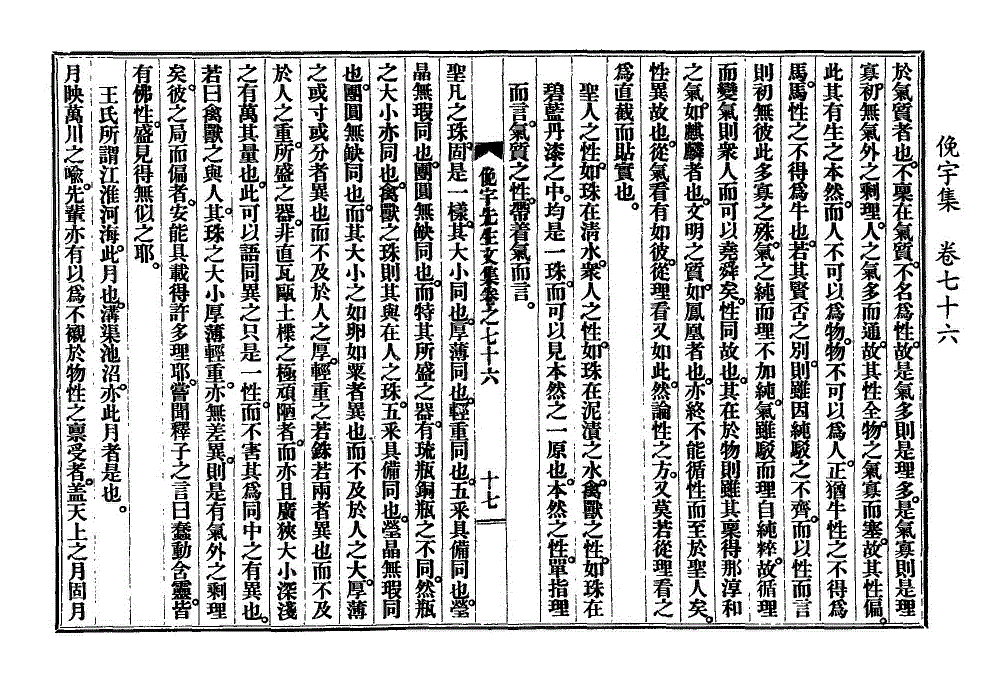 于气质者也。不禀在气质。不名为性。故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寡则是理寡。初无气外之剩理。人之气多而通。故其性全。物之气寡而塞。故其性偏。此其有生之本然。而人不可以为物。物不可以为人。正犹牛性之不得为马。马性之不得为牛也。若其贤否之别。则虽因纯驳之不齐。而以性而言则初无彼此多寡之殊。气之纯而理不加纯。气虽驳而理自纯粹。故循理而变气则众人而可以尧舜矣。性同故也。其在于物则虽其禀得那淳和之气。如麒麟者也。文明之质。如凤凰者也。亦终不能循性而至于圣人矣。性异故也。从气看有如彼。从理看又如此。然论性之方。又莫若从理看之为直截而贴实也。
于气质者也。不禀在气质。不名为性。故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寡则是理寡。初无气外之剩理。人之气多而通。故其性全。物之气寡而塞。故其性偏。此其有生之本然。而人不可以为物。物不可以为人。正犹牛性之不得为马。马性之不得为牛也。若其贤否之别。则虽因纯驳之不齐。而以性而言则初无彼此多寡之殊。气之纯而理不加纯。气虽驳而理自纯粹。故循理而变气则众人而可以尧舜矣。性同故也。其在于物则虽其禀得那淳和之气。如麒麟者也。文明之质。如凤凰者也。亦终不能循性而至于圣人矣。性异故也。从气看有如彼。从理看又如此。然论性之方。又莫若从理看之为直截而贴实也。圣人之性。如珠在清水。众人之性。如珠在泥渍之水。禽兽之性。如珠在碧蓝丹漆之中。均是一珠。而可以见本然之一原也。本然之性。单指理而言。气质之性。带着气而言。
圣凡之珠。固是一样。其大小同也。厚薄同也。轻重同也。五采具备同也。莹晶无瑕同也。团圆无缺同也。而特其所盛之器。有琉瓶铜瓶之不同。然瓶之大小亦同也。禽兽之珠则其与在人之珠。五采具备同也。莹晶无瑕同也。团圆无缺同也。而其大小之如卵如粟者异也而不及于人之大。厚薄之或寸或分者异也而不及于人之厚。轻重之若铢若两者异也而不及于人之重。所盛之器。非直瓦瓯土楪之极顽陋者。而亦且广狭大小深浅之有万其量也。此可以语同异之只是一性。而不害其为同中之有异也。若曰禽兽之与人。其珠之大小厚薄轻重。亦无差异。则是有气外之剩理矣。彼之局而偏者。安能具载得许多理耶。尝闻释子之言曰蠢动含灵。皆有佛性。盛见得无似之耶。
王氏所谓江淮河海。此月也。沟渠池沼。亦此月者是也。
月映万川之喻。先辈亦有以为不衬于物性之禀受者。盖天上之月固月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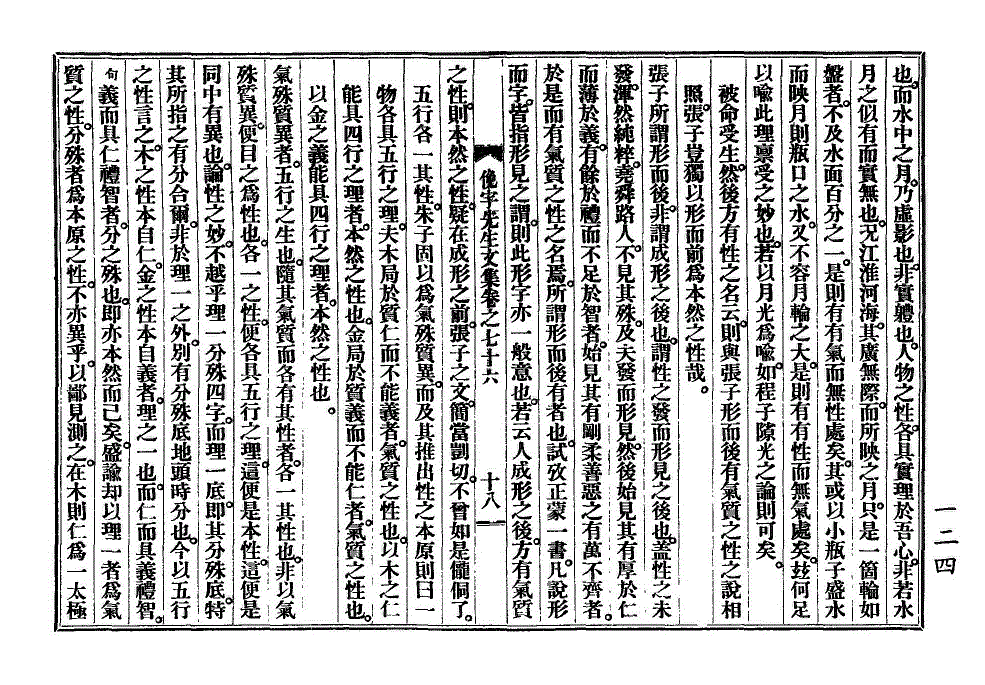 也。而水中之月。乃虚影也。非实体也。人物之性。各具实理于吾心。非若水月之似有而实无也。况江淮河海。其广无际。而所映之月。只是一个轮如盘者。不及水面百分之一。是则有有气而无性处矣。其或以小瓶子盛水而映月则瓶口之水。又不容月轮之大。是则有有性而无气处矣。玆何足以喻此理盖受之妙也。若以月光为喻。如程子隙光之论则可矣。
也。而水中之月。乃虚影也。非实体也。人物之性。各具实理于吾心。非若水月之似有而实无也。况江淮河海。其广无际。而所映之月。只是一个轮如盘者。不及水面百分之一。是则有有气而无性处矣。其或以小瓶子盛水而映月则瓶口之水。又不容月轮之大。是则有有性而无气处矣。玆何足以喻此理盖受之妙也。若以月光为喻。如程子隙光之论则可矣。被命受生。然后方有性之名云。则与张子形而后有气质之性之说相照。张子岂独以形而前为本然之性哉。
张子所谓形而后。非谓成形之后也。谓性之发而形见之后也。盖性之未发。浑然纯粹。尧舜路人。不见其殊。及夫发而形见。然后始见其有厚于仁而薄于义。有馀于礼而不足于智者。始见其有刚柔善恶之有万不齐者。于是而有气质之性之名焉。所谓形而后有者也。试考正蒙一书。凡说形而字。皆指形见之谓。则此形字亦一般意也。若云人成形之后。方有气质之性。则本然之性。疑在成形之前。张子之文。简当剀切。不曾如是儱侗了。
五行各一其性。朱子固以为气殊质异。而及其推出性之本原则曰一物各具五行之理。夫木局于质仁而不能义者。气质之性也。以木之仁能具四行之理者。本然之性也。金局于质义而不能仁者。气质之性也。以金之义能具四行之理者。本然之性也。
气殊质异者。五行之生也。随其气质而各有其性者。各一其性也。非以气殊质异。便目之为性也。各一之性。便各具五行之理。这便是本性。这便是同中有异也。论性之妙。不越乎理一分殊四字。而理一底。即其分殊底。特其所指之有分合尔。非于理一之外。别有分殊底地头时分也。今以五行之性言之。木之性本自仁。金之性本自义者。理之一也。而仁而具义礼智。(句)义而具仁礼智者。分之殊也。即亦本然而已矣。盛谕却以理一者为气质之性。分殊者为本原之性。不亦异乎。以鄙见测之。在木则仁为一太极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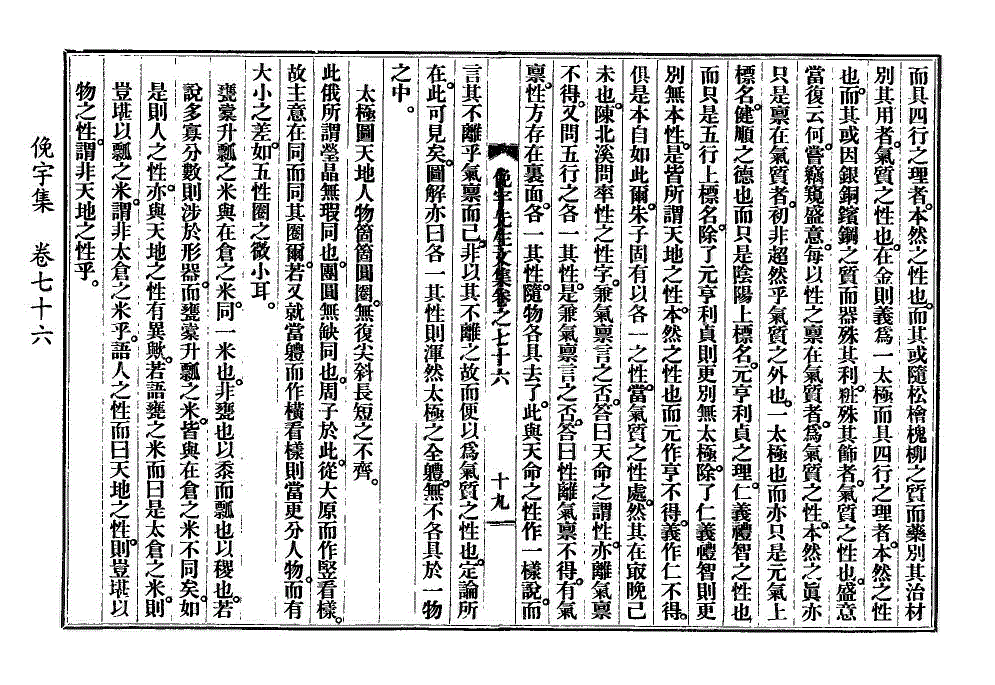 而具四行之理者。本然之性也。而其或随松桧槐柳之质而药别其治材别其用者。气质之性也。在金则义为一太极而具四行之理者。本然之性也。而其或因银铜镔钢之质而器殊其利。妆殊其饰者。气质之性也。盛意当复云何。尝窃窥盛意。每以性之禀在气质者。为气质之性。本然之真亦只是禀在气质者。初非超然乎气质之外也。一太极也而亦只是元气上标名。健顺之德也而只是阴阳上标名。元亨利贞之理。仁义礼智之性也而只是五行上标名。除了元亨利贞则更别无太极。除了仁义礼智则更别无本性。是皆所谓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也而元作亨不得。义作仁不得。俱是本自如此尔。朱子固有以各一之性。当气质之性处。然其在最晚己未也。陈北溪问率性之性字。兼气禀言之否。答曰天命之谓性。亦离气禀不得。又问五行之各一其性。是兼气禀言之否。答曰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各一其性。随物各具去了。此与天命之性作一样说。而言其不离乎气禀而已。非以其不离之故而便以为气质之性也。定论所在。此可见矣。图解亦曰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
而具四行之理者。本然之性也。而其或随松桧槐柳之质而药别其治材别其用者。气质之性也。在金则义为一太极而具四行之理者。本然之性也。而其或因银铜镔钢之质而器殊其利。妆殊其饰者。气质之性也。盛意当复云何。尝窃窥盛意。每以性之禀在气质者。为气质之性。本然之真亦只是禀在气质者。初非超然乎气质之外也。一太极也而亦只是元气上标名。健顺之德也而只是阴阳上标名。元亨利贞之理。仁义礼智之性也而只是五行上标名。除了元亨利贞则更别无太极。除了仁义礼智则更别无本性。是皆所谓天地之性。本然之性也而元作亨不得。义作仁不得。俱是本自如此尔。朱子固有以各一之性。当气质之性处。然其在最晚己未也。陈北溪问率性之性字。兼气禀言之否。答曰天命之谓性。亦离气禀不得。又问五行之各一其性。是兼气禀言之否。答曰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各一其性。随物各具去了。此与天命之性作一样说。而言其不离乎气禀而已。非以其不离之故而便以为气质之性也。定论所在。此可见矣。图解亦曰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太极图天地人物个个圆圈。无复尖斜长短之不齐。
此俄所谓莹晶无瑕同也。团圆无缺同也。周子于此。从大原而作竖看样。故主意在同而同其圈尔。若又就当体而作横看样则当更分人物。而有大小之差。如五性圈之微小耳。
瓮橐升瓢之米与在仓之米。同一米也。非瓮也以黍而瓢也以稷也。若说多寡分数则涉于形器。而瓮橐升瓢之米。皆与在仓之米不同矣。如是则人之性。亦与天地之性有异欤。若语瓮之米而曰是太仓之米。则岂堪以瓢之米。谓非太仓之米乎。语人之性而曰天地之性。则岂堪以物之性。谓非天地之性乎。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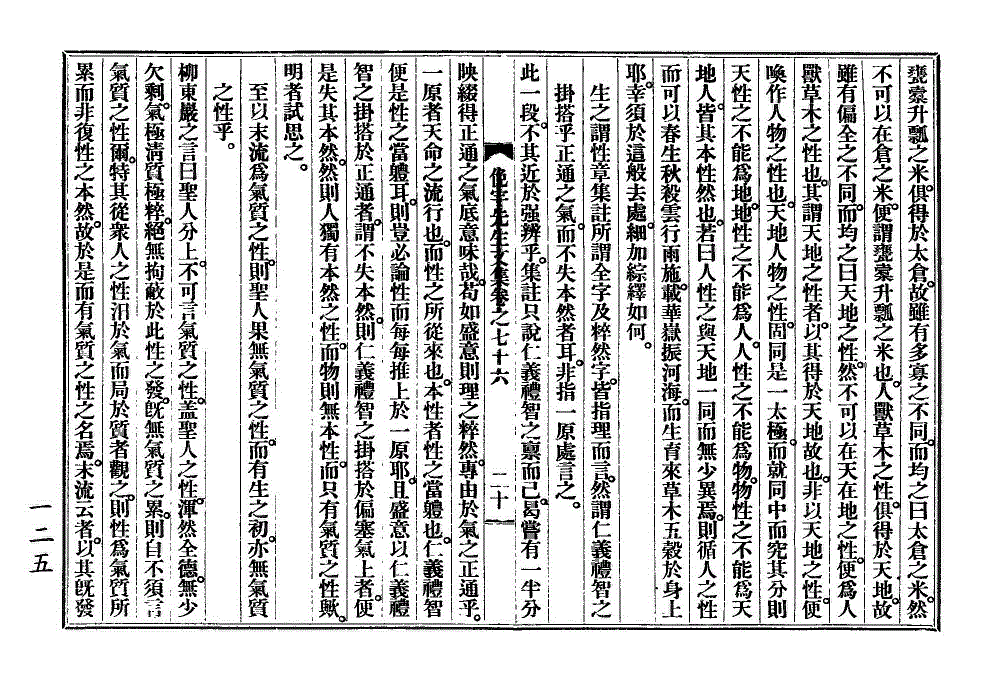 瓮橐升瓢之米。俱得于太仓。故虽有多寡之不同。而均之曰太仓之米。然不可以在仓之米。便谓瓮橐升瓢之米也。人兽草木之性。俱得于天地。故虽有偏全之不同。而均之曰天地之性。然不可以在天在地之性。便为人兽草木之性也。其谓天地之性者。以其得于天地故也。非以天地之性。便唤作人物之性也。天地人物之性。固同是一太极。而就同中而究其分则天性之不能为地。地性之不能为人。人性之不能为物。物性之不能为天地人。皆其本性然也。若曰人性之与天地一同而无少异焉。则循人之性而可以春生秋杀云行雨施。载华岳振河海。而生育来草木五谷于身上耶。幸须于这般去处。细加综绎如何。
瓮橐升瓢之米。俱得于太仓。故虽有多寡之不同。而均之曰太仓之米。然不可以在仓之米。便谓瓮橐升瓢之米也。人兽草木之性。俱得于天地。故虽有偏全之不同。而均之曰天地之性。然不可以在天在地之性。便为人兽草木之性也。其谓天地之性者。以其得于天地故也。非以天地之性。便唤作人物之性也。天地人物之性。固同是一太极。而就同中而究其分则天性之不能为地。地性之不能为人。人性之不能为物。物性之不能为天地人。皆其本性然也。若曰人性之与天地一同而无少异焉。则循人之性而可以春生秋杀云行雨施。载华岳振河海。而生育来草木五谷于身上耶。幸须于这般去处。细加综绎如何。生之谓性章集注所谓全字及粹然字。皆指理而言。然谓仁义礼智之挂搭乎正通之气。而不失本然者耳。非指一原处言之。
此一段。不其近于强辨乎。集注只说仁义礼智之禀而已。曷尝有一半分映缀得正通之气底意味哉。苟如盛意则理之粹然。专由于气之正通乎。一原者天命之流行也。而性之所从来也。本性者性之当体也。仁义礼智便是性之当体耳。则岂必论性而每每推上于一原耶。且盛意以仁义礼智之挂搭于正通者。谓不失本然。则仁义礼智之挂搭于偏塞气上者。便是失其本然。然则人独有本然之性。而物则无本性。而只有气质之性欤。明者试思之。
至以末流为气质之性。则圣人果无气质之性。而有生之初。亦无气质之性乎。
柳东岩之言曰圣人分上。不可言气质之性。盖圣人之性。浑然全德。无少欠剩。气极清质极粹。绝无拘蔽于此性之发。既无气质之累。则自不须言气质之性尔。特其从众人之性汩于气而局于质者观之。则性为气质所累而非复性之本然。故于是而有气质之性之名焉。末流云者。以其既发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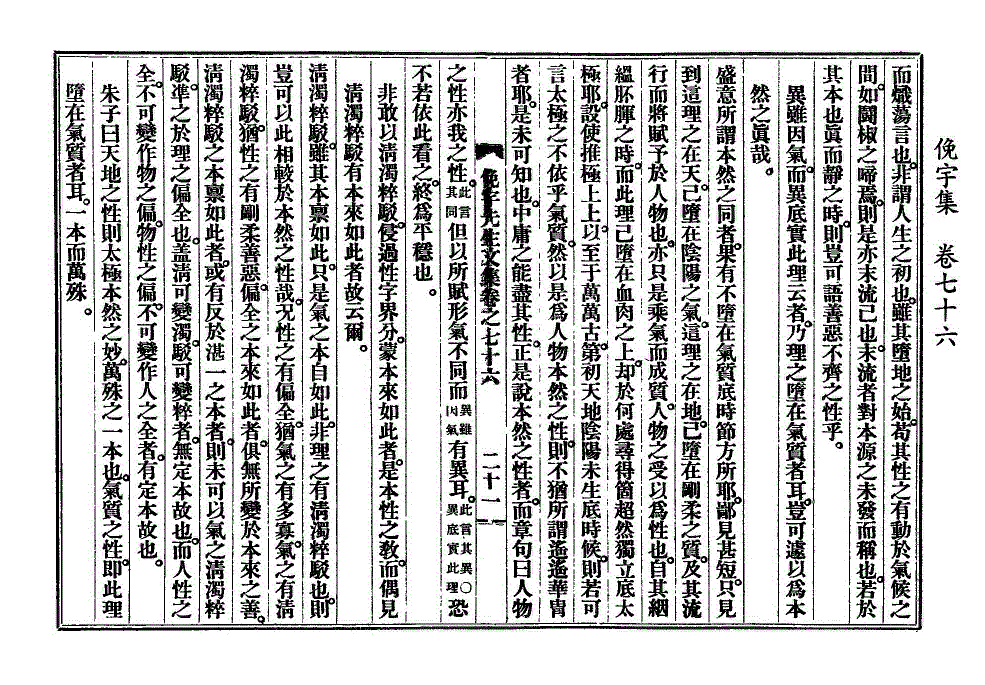 而炽荡言也。非谓人生之初也。虽其堕地之始。苟其性之有动于气候之间。如斗椒之啼焉。则是亦末流已也。末流者对本源之未发而称也。若于其本也真而静之时。则岂可语善恶不齐之性乎。
而炽荡言也。非谓人生之初也。虽其堕地之始。苟其性之有动于气候之间。如斗椒之啼焉。则是亦末流已也。末流者对本源之未发而称也。若于其本也真而静之时。则岂可语善恶不齐之性乎。异虽因气。而异底实此理云者。乃理之堕在气质者耳。岂可遽以为本然之真哉。
盛意所谓本然之同者。果有不堕在气质底时节方所耶。鄙见甚短。只见到这理之在天。已堕在阴阳之气。这理之在地。已堕在刚柔之质。及其流行而将赋予于人物也。亦只是乘气而成质。人物之受以为性也。自其絪缊胚腪之时。而此理已堕在血肉之上。却于何处寻得个超然独立底太极耶。设使推极上上。以至于万万古。第初天地阴阳未生底时候。则若可言太极之不依乎气质。然以是为人物本然之性。则不犹所谓遥遥华胄者耶。是未可知也。中庸之能尽其性。正是说本然之性者。而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言其同)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异虽因气)有异耳。(此言其异○异底实此理)恐不若依此看之。终为平稳也。
非敢以清浊粹驳。侵过性字界分。蒙本来如此者。是本性之教。而偶见清浊粹驳有本来如此者故云尔。
清浊粹驳。虽其本禀如此。只是气之本自如此。非理之有清浊粹驳也。则岂可以此相较于本然之性哉。况性之有偏全。犹气之有多寡。气之有清浊粹驳。犹性之有刚柔善恶。偏全之本来如此者。俱无所变于本来之善。清浊粹驳之本禀如此者。或有反于湛一之本者。则未可以气之清浊粹驳。准之于理之偏全也。盖清可变浊。驳可变粹者。无定本故也。而人性之全。不可变作物之偏。物性之偏。不可变作人之全者。有定本故也。
朱子曰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即此理堕在气质者耳。一本而万殊。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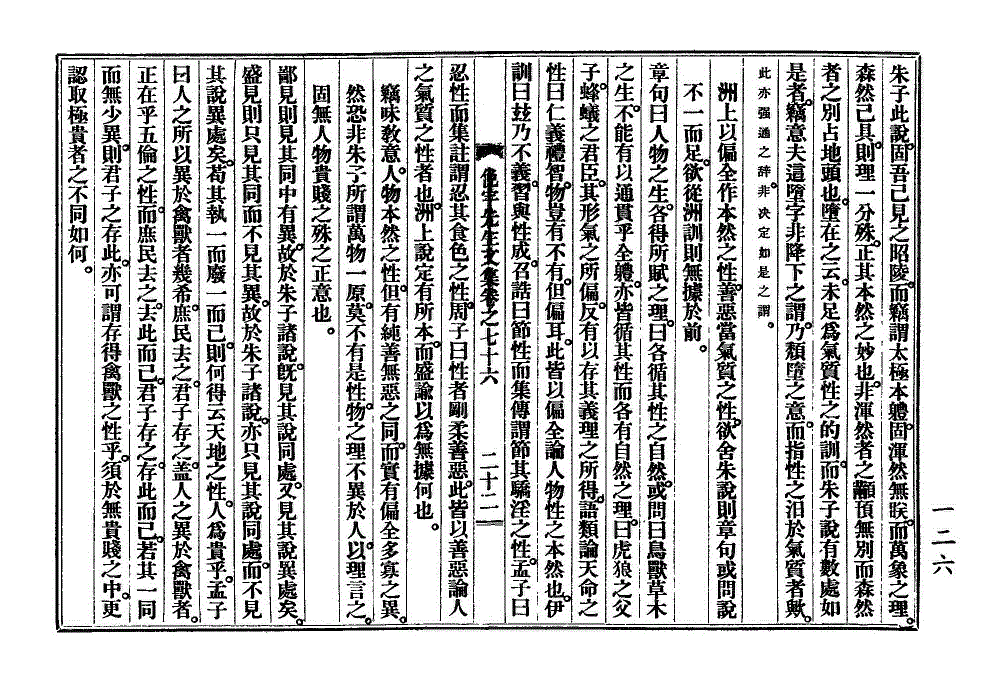 朱子此说。固吾已见之昭陵。而窃谓太极本体。固浑然无眹。而万象之理。森然已具。则理一分殊。正其本然之妙也。非浑然者之颟顸无别而森然者之别占地头也。堕在之云。未足为气质性之的训。而朱子说有数处如是者。窃意夫这堕字非降下之谓。乃颓堕之意。而指性之汩于气质者欤。(此亦强通之辞。非决定如是之谓。)
朱子此说。固吾已见之昭陵。而窃谓太极本体。固浑然无眹。而万象之理。森然已具。则理一分殊。正其本然之妙也。非浑然者之颟顸无别而森然者之别占地头也。堕在之云。未足为气质性之的训。而朱子说有数处如是者。窃意夫这堕字非降下之谓。乃颓堕之意。而指性之汩于气质者欤。(此亦强通之辞。非决定如是之谓。)洲上以偏全作本然之性。善恶当气质之性。欲舍朱说则章句或问说不一而足。欲从洲训则无据于前。
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所赋之理。曰各循其性之自然。或问曰鸟兽草木之生。不能有以通贯乎全体。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曰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其形气之所偏。反有以存其义理之所得。语类论天命之性曰仁义礼智。物岂有不有。但偏耳。此皆以偏全论人物性之本然也。伊训曰玆乃不义。习与性成。召诰曰节性而集传谓节其骄淫之性。孟子曰忍性而集注谓忍其食色之性。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此皆以善恶论人之气质之性者也。洲上说定有所本。而盛谕以为无据何也。
窃味教意。人物本然之性。但有纯善无恶之同。而实有偏全多寡之异。然恐非朱子所谓万物一原。莫不有是性。物之理不异于人。以理言之。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之正意也。
鄙见则见其同中有异。故于朱子诸说。既见其说同处。又见其说异处矣。盛见则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故于朱子诸说。亦只见其说同处。而不见其说异处矣。苟其执一而废一而已。则何得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乎。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盖人之异于禽兽者。正在乎五伦之性。而庶民去之。去此而已。君子存之。存此而已。若其一同而无少异。则君子之存此。亦可谓存得禽兽之性乎。须于无贵贱之中。更认取极贵者之不同如何。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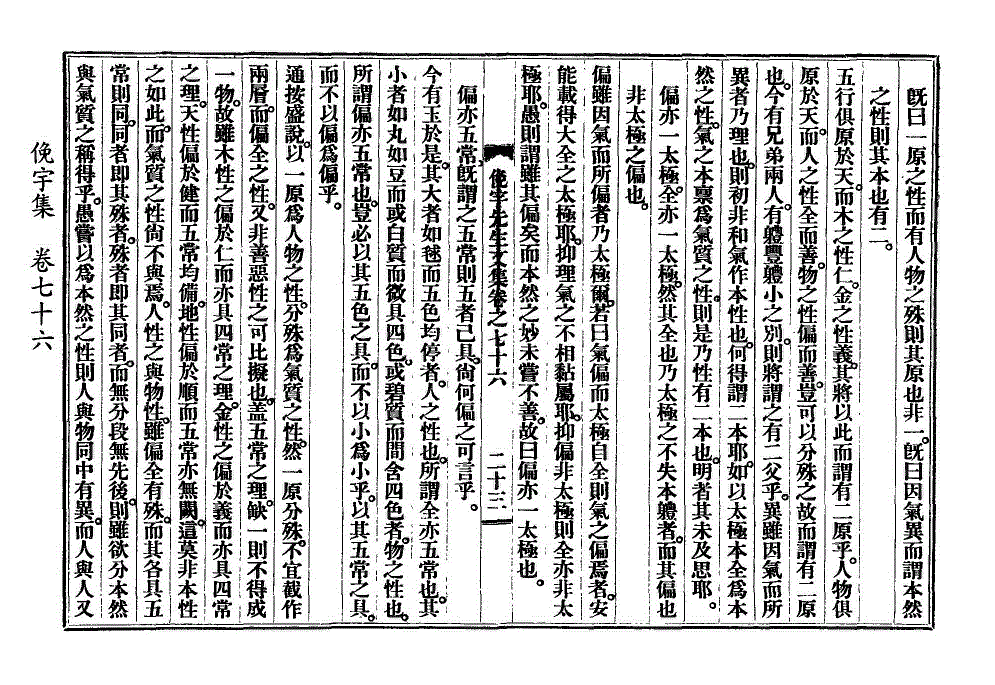 既曰一原之性而有人物之殊则其原也非一。既曰因气异而谓本然之性则其本也有二。
既曰一原之性而有人物之殊则其原也非一。既曰因气异而谓本然之性则其本也有二。五行俱原于天。而木之性仁。金之性义。其将以此而谓有二原乎。人物俱原于天。而人之性全而善。物之性偏而善。岂可以分殊之故而谓有二原也。今有兄弟两人。有体丰体小之别。则将谓之有二父乎。异虽因气而所异者乃理也。则初非和气作本性也。何得谓二本耶。如以太极本全为本然之性。气之本禀为气质之性。则是乃性有二本也。明者其未及思耶。
偏亦一太极。全亦一太极。然其全也乃太极之不失本体者。而其偏也。非太极之偏也。
偏虽因气而所偏者乃太极尔。若曰气偏而太极自全则气之偏焉者。安能载得大全之太极耶。抑理气之不相黏属耶。抑偏非太极则全亦非太极耶。愚则谓虽其偏矣而本然之妙未尝不善。故曰偏亦一太极也。
偏亦五常。既谓之五常则五者已具。尚何偏之可言乎。
今有玉于是。其大者如毬而五色均停者。人之性也。所谓全亦五常也。其小者如丸如豆而或白质而微具四色。或碧质而间含四色者。物之性也。所谓偏亦五常也。岂必以其五色之具。而不以小为小乎。以其五常之具。而不以偏为偏乎。
通按盛说。以一原为人物之性。分殊为气质之性。然一原分殊。不宜截作两层。而偏全之性。又非善恶性之可比拟也。盖五常之理。缺一则不得成一物。故虽木性之偏于仁而亦具四常之理。金性之偏于义而亦具四常之理。天性偏于健而五常均备。地性偏于顺而五常亦无阙。这莫非本性之如此。而气质之性尚不与焉。人性之与物性。虽偏全有殊。而其各具五常则同。同者即其殊者。殊者即其同者。而无分段无先后。则虽欲分本然与气质之称得乎。愚尝以为本然之性则人与物同中有异。而人与人又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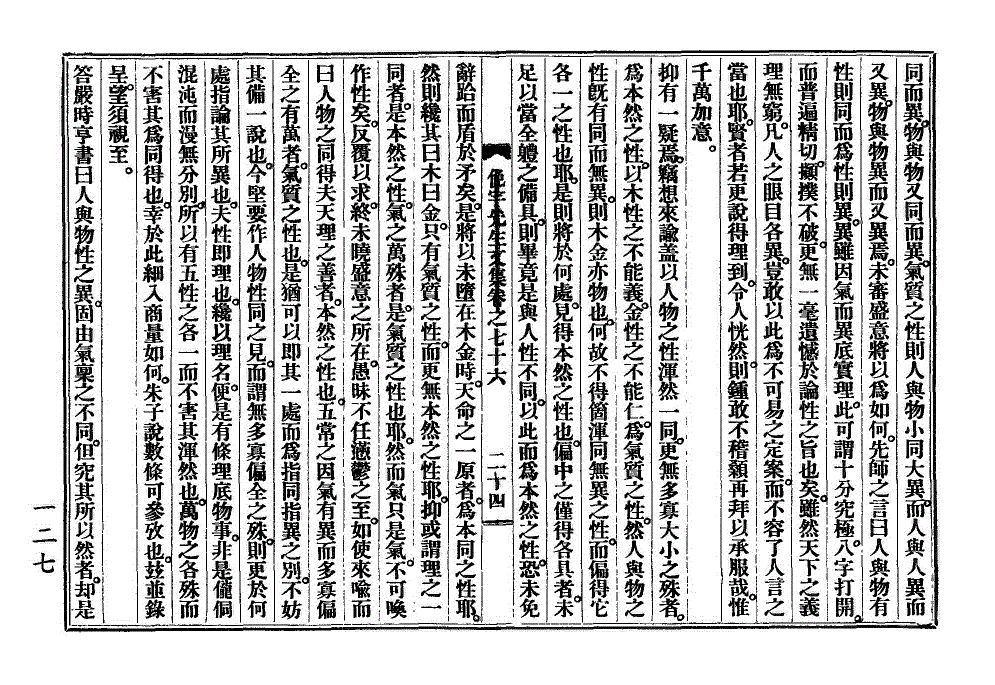 同而异。物与物又同而异。气质之性则人与物小同大异。而人与人异而又异。物与物异而又异焉。未审盛意将以为如何。先师之言曰人与物有性则同而为性则异。异虽因气而异底实理。此可谓十分究极。八字打开。而普遍精切。攧扑不破。更无一毫遗憾于论性之旨也矣。虽然天下之义理无穷。凡人之眼目各异。岂敢以此为不可易之定案。而不容了人言之当也耶。贤者若更说得理到。令人恍然。则钟敢不稽颡再拜以承服哉。惟千万加意。
同而异。物与物又同而异。气质之性则人与物小同大异。而人与人异而又异。物与物异而又异焉。未审盛意将以为如何。先师之言曰人与物有性则同而为性则异。异虽因气而异底实理。此可谓十分究极。八字打开。而普遍精切。攧扑不破。更无一毫遗憾于论性之旨也矣。虽然天下之义理无穷。凡人之眼目各异。岂敢以此为不可易之定案。而不容了人言之当也耶。贤者若更说得理到。令人恍然。则钟敢不稽颡再拜以承服哉。惟千万加意。抑有一疑焉。窃想来谕盖以人物之性浑然一同。更无多寡大小之殊者。为本然之性。以木性之不能义。金性之不能仁。为气质之性。然人与物之性既有同而无异。则木金亦物也。何故不得个浑同无异之性。而偏得它各一之性也耶。是则将于何处。见得本然之性也。偏中之仅得各具者。未足以当全体之备具。则毕竟是与人性不同。以此而为本然之性。恐未免辞跲而盾于矛矣。是将以未堕在木金时。天命之一原者。为本同之性耶。然则才其曰木曰金。只有气质之性。而更无本然之性耶。抑或谓理之一同者。是本然之性。气之万殊者。是气质之性也耶。然而气只是气。不可唤作性矣。反覆以求。终未晓盛意之所在。愚昧不任懑郁之至。如使来喻而曰人物之同得夫天理之善者。本然之性也。五常之因气有异而多寡偏全之有万者。气质之性也。是犹可以即其一处而为指同指异之别。不妨其备一说也。今坚要作人物性同之见。而谓无多寡偏全之殊。则更于何处指论其所异也。夫性即理也。才以理名。便是有条理底物事。非是儱侗混沌而漫无分别。所以有五性之各一而不害其浑然也。万物之各殊而不害其为同得也。幸于此细入商量如何。朱子说数条可参考也。玆并录呈。望须视至。
答严时亨书曰人与物性之异。固由气禀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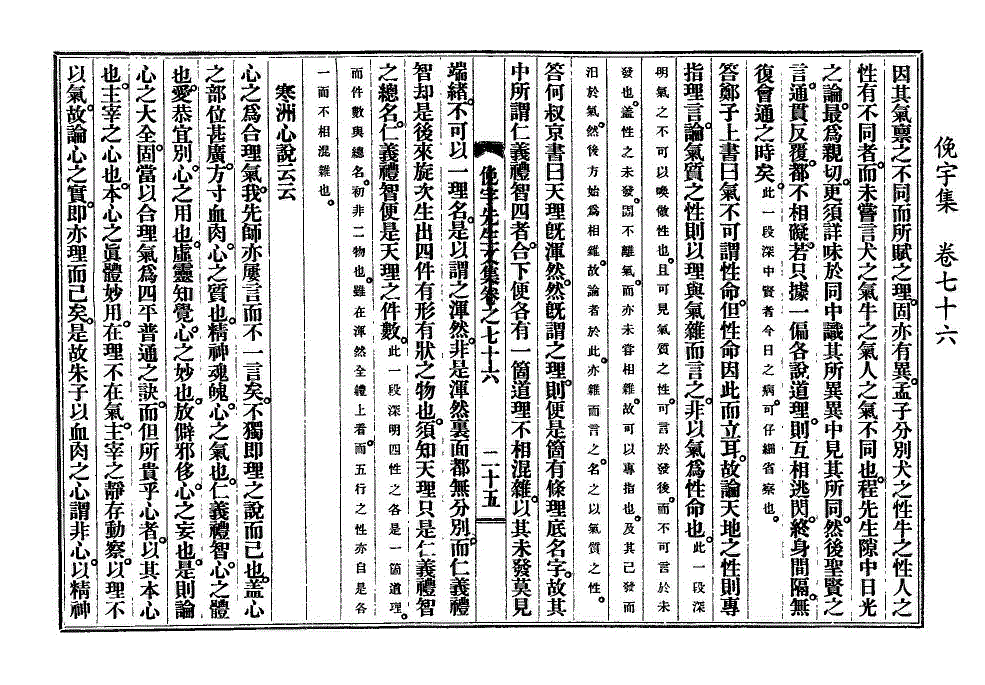 因其气禀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尝言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不同也。程先生隙中日光之论。最为亲切。更须详味于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然后圣贤之言。通贯反覆。都不相碍。若只据一偏各说道理。则互相逃闪。终身间隔。无复会通之时矣。(此一段深中贤者今日之病。可仔细省察也。)
因其气禀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尝言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不同也。程先生隙中日光之论。最为亲切。更须详味于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然后圣贤之言。通贯反覆。都不相碍。若只据一偏各说道理。则互相逃闪。终身间隔。无复会通之时矣。(此一段深中贤者今日之病。可仔细省察也。)答郑子上书曰气不可谓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非以气为性命也。(此一段深明气之不可以唤做性也。且可见气质之性。可言于发后。而不可言于未发也。盖性之未发。固不离气。而亦未尝相杂。故可以专指也。及其已发而汩于气。然后方始为相杂。故论者于此。亦杂而言之。名之以气质之性。)
答何叔京书曰天理既浑然。然既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却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此一段深明四性之各是一个道理。而件数与总名。初非二物也。虽在浑然全体上看。而五行之性亦自是各一而不相混杂也。)
寒洲心说云云
心之为合理气。我先师亦屡言而不一言矣。不独即理之说而已也。盖心之部位甚广。方寸血肉。心之质也。精神魂魄。心之气也。仁义礼智。心之体也。爱恭宜别。心之用也。虚灵知觉。心之妙也。放僻邪侈。心之妄也。是则论心之大全。固当以合理气为四平普通之诀。而但所贵乎心者。以其本心也。主宰之心也。本心之真体妙用。在理不在气。主宰之静存动察。以理不以气。故论心之实。即亦理而已矣。是故朱子以血肉之心谓非心。以精神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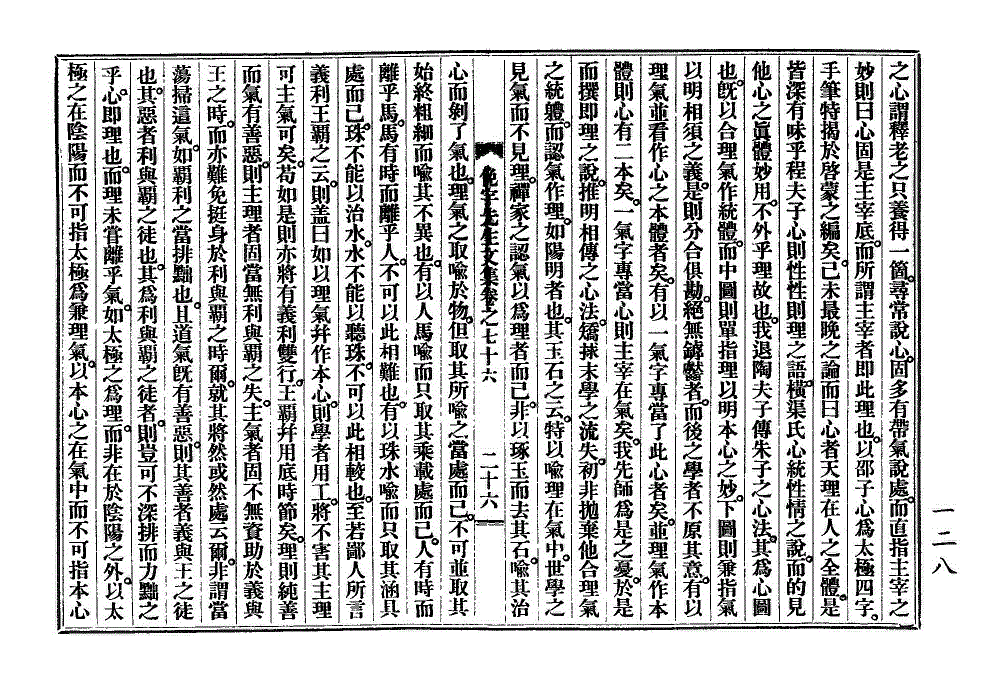 之心谓释老之只养得一个。寻常说心。固多有带气说处。而直指主宰之妙则曰心固是主宰底。而所谓主宰者即此理也。以邵子心为太极四字。手笔特揭于启蒙之编矣。己未最晚之论而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是皆深有味乎程夫子心则性性则理之语。横渠氏心统性情之说。而的见他心之真体妙用。不外乎理故也。我退陶夫子传朱子之心法。其为心图也。既以合理气作统体。而中图则单指理以明本心之妙。下图则兼指气以明相须之义。是则分合俱勘。绝无罅齾者。而后之学者不原其意。有以理气并看作心之本体者矣。有以一气字专当了此心者矣。并理气作本体则心有二本矣。一气字专当心则主宰在气矣。我先师为是之忧。于是而撰即理之说。推明相传之心法。矫救末学之流失。初非抛弃他合理气之统体。而认气作理。如阳明者也。其玉石之云。特以喻理在气中。世学之见气而不见理。禅家之认气以为理者而已。非以琢玉而去其石。喻其治心而剥了气也。理气之取喻于物。但取其所喻之当处而已。不可并取其始终粗细而喻其不异也。有以人马喻而只取其乘载处而已。人有时而离乎马。马有时而离乎人。不可以此相难也。有以珠水喻而只取其涵具处而已。珠不能以治水。水不能以听珠。不可以此相较也。至若鄙人所言义利王霸之云。则盖曰如以理气并作本心。则学者用工。将不害其主理可主气可矣。苟如是则亦将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底时节矣。理则纯善而气有善恶。则主理者固当无利与霸之失。主气者固不无资助于义与王之时。而亦难免挺身于利与霸之时尔。就其将然或然处云尔。非谓当荡扫这气。如霸利之当排黜也。且道气既有善恶。则其善者义与王之徒也。其恶者利与霸之徒也。其为利与霸之徒者。则岂可不深排而力黜之乎。心即理也。而理未尝离乎气。如太极之为理。而非在于阴阳之外。以太极之在阴阳而不可指太极为兼理气。以本心之在气中而不可指本心
之心谓释老之只养得一个。寻常说心。固多有带气说处。而直指主宰之妙则曰心固是主宰底。而所谓主宰者即此理也。以邵子心为太极四字。手笔特揭于启蒙之编矣。己未最晚之论而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是皆深有味乎程夫子心则性性则理之语。横渠氏心统性情之说。而的见他心之真体妙用。不外乎理故也。我退陶夫子传朱子之心法。其为心图也。既以合理气作统体。而中图则单指理以明本心之妙。下图则兼指气以明相须之义。是则分合俱勘。绝无罅齾者。而后之学者不原其意。有以理气并看作心之本体者矣。有以一气字专当了此心者矣。并理气作本体则心有二本矣。一气字专当心则主宰在气矣。我先师为是之忧。于是而撰即理之说。推明相传之心法。矫救末学之流失。初非抛弃他合理气之统体。而认气作理。如阳明者也。其玉石之云。特以喻理在气中。世学之见气而不见理。禅家之认气以为理者而已。非以琢玉而去其石。喻其治心而剥了气也。理气之取喻于物。但取其所喻之当处而已。不可并取其始终粗细而喻其不异也。有以人马喻而只取其乘载处而已。人有时而离乎马。马有时而离乎人。不可以此相难也。有以珠水喻而只取其涵具处而已。珠不能以治水。水不能以听珠。不可以此相较也。至若鄙人所言义利王霸之云。则盖曰如以理气并作本心。则学者用工。将不害其主理可主气可矣。苟如是则亦将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底时节矣。理则纯善而气有善恶。则主理者固当无利与霸之失。主气者固不无资助于义与王之时。而亦难免挺身于利与霸之时尔。就其将然或然处云尔。非谓当荡扫这气。如霸利之当排黜也。且道气既有善恶。则其善者义与王之徒也。其恶者利与霸之徒也。其为利与霸之徒者。则岂可不深排而力黜之乎。心即理也。而理未尝离乎气。如太极之为理。而非在于阴阳之外。以太极之在阴阳而不可指太极为兼理气。以本心之在气中而不可指本心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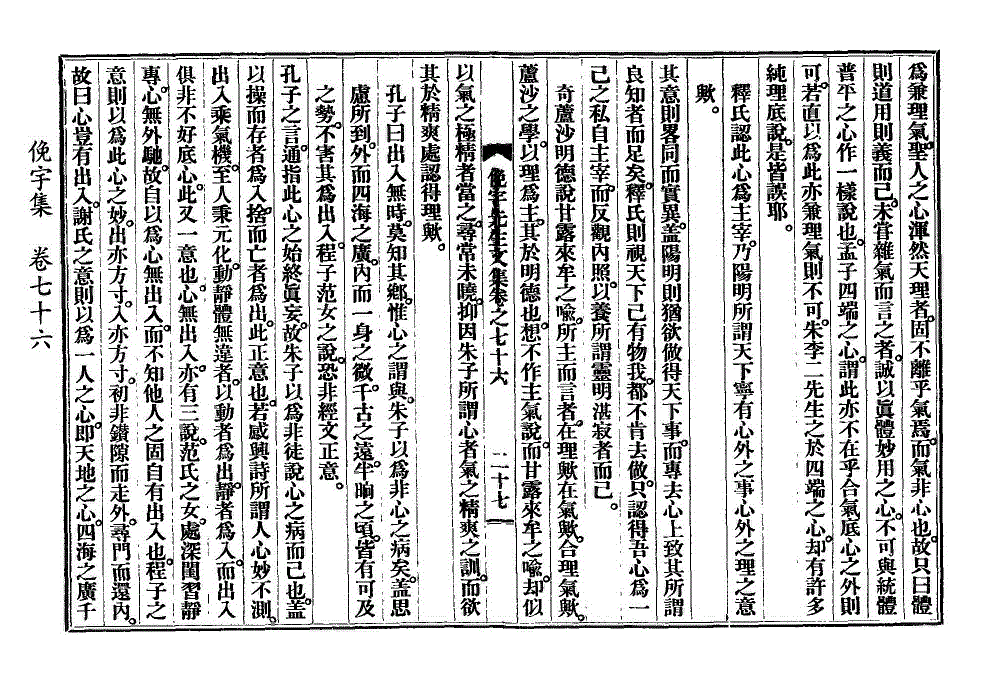 为兼理气。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者。固不离乎气焉。而气非心也。故只曰体则道用则义而已。未尝杂气而言之者。诚以真体妙用之心。不可与统体普平之心作一样说也。孟子四端之心。谓此亦不在乎合气底心之外则可。若直以为此亦兼理气则不可。朱李二先生之于四端之心。却有许多纯理底说。是皆误耶。
为兼理气。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者。固不离乎气焉。而气非心也。故只曰体则道用则义而已。未尝杂气而言之者。诚以真体妙用之心。不可与统体普平之心作一样说也。孟子四端之心。谓此亦不在乎合气底心之外则可。若直以为此亦兼理气则不可。朱李二先生之于四端之心。却有许多纯理底说。是皆误耶。释氏认此心为主宰。乃阳明所谓天下宁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之意欤。
其意则略同而实异。盖阳明则犹欲做得天下事。而专去心上致其所谓良知者而足矣。释氏则视天下已有物。我都不肯去做。只认得吾心为一己之私自主宰。而反观内照。以养所谓灵明湛寂者而已。
奇芦沙明德说甘露来牟之喻。所主而言者。在理欤在气欤。合理气欤。
芦沙之学。以理为主。其于明德也。想不作主气说。而甘露来牟之喻。却似以气之极精者当之。寻常未晓。抑因朱子所谓心者气之精爽之训。而欲其于精爽处认得理欤。
孔子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朱子以为非心之病矣。盖思虑所到。外而四海之广。内而一身之微。千古之远。半晌之顷。皆有可及之势。不害其为出入。程子范女之说。恐非经文正意。
孔子之言。通指此心之始终真妄。故朱子以为非徒说心之病而已也。盖以操而存者为入。舍而亡者为出。此正意也。若感兴诗所谓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者。以动者为出。静者为入。而出入俱非不好底心。此又一意也。心无出入。亦有三说。范氏之女。处深闺习静专。心无外驰。故自以为心无出入。而不知他人之固自有出入也。程子之意则以为此心之妙。出亦方寸。入亦方寸。初非钻隙而走外。寻门而还内。故曰心岂有出入。谢氏之意则以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四海之广千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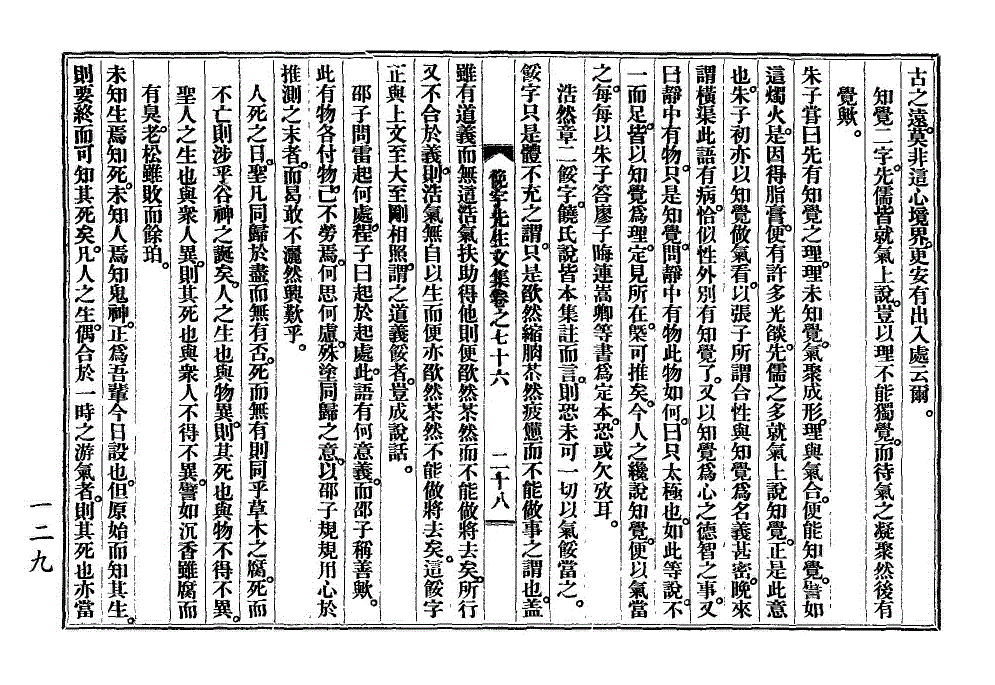 古之远。莫非这心境界。更安有出入处云尔。
古之远。莫非这心境界。更安有出入处云尔。知觉二字。先儒皆就气上说。岂以理不能独觉。而待气之凝聚然后有觉欤。
朱子尝曰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脂膏。便有许多光燄。先儒之多就气上说知觉。正是此意也。朱子初亦以知觉做气看。以张子所谓合性与知觉为名义甚密。晚来谓横渠此语有病。恰似性外别有知觉了。又以知觉为心之德智之事。又曰静中有物。只是知觉。问静中有物此物如何。曰只太极也。如此等说。不一而足。皆以知觉为理。定见所在。槩可推矣。今人之才说知觉。便以气当之。每每以朱子答廖子晦连嵩卿等书为定本。恐或欠考耳。
浩然章二馁字。饶氏说皆本集注而言。则恐未可一切以气馁当之。
馁字只是体不充之谓。只是欿然缩朒苶然疲惫而不能做事之谓也。盖虽有道义而无这浩气扶助得他则便欿然苶然而不能做将去矣。所行又不合于义。则浩气无自以生而便亦欿然苶然不能做将去矣。这馁字正与上文至大至刚相照。谓之道义馁者。岂成说话。
邵子问雷起何处。程子曰起于起处。此语有何意义。而邵子称善欤。
此有物各付物。已不劳焉。何思何虑。殊涂同归之意。以邵子规规用心于推测之末者。而曷敢不洒然兴叹乎。
人死之日。圣凡同归于尽而无有否。死而无有则同乎草木之腐。死而不亡则涉乎谷神之诞矣。人之生也与物异。则其死也与物不得不异。圣人之生也与众人异。则其死也与众人不得不异。譬如沉香虽腐而有臭。老松虽败而馀珀。
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神。正为吾辈今日设也。但原始而知其生。则要终而可知其死矣。凡人之生。偶合于一时之游气者。则其死也亦当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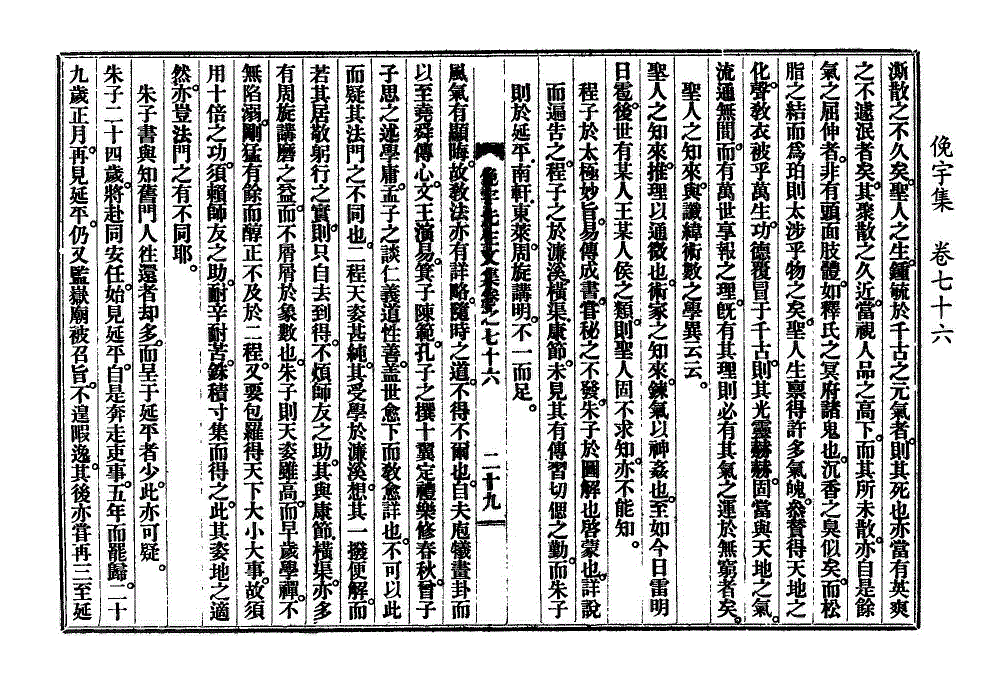 澌散之不久矣。圣人之生。钟毓于千古之元气者。则其死也亦当有英爽之不遽泯者矣。其聚散之久近。当视人品之高下。而其所未散。亦自是馀气之屈伸者。非有头面肢体。如释氏之冥府诸鬼也。沉香之臭似矣。而松脂之结而为珀则太涉乎物之矣。圣人生禀得许多气魄。参赞得天地之化。声教衣被乎万生。功德覆冒于千古。则其光灵赫赫。固当与天地之气。流通无间。而有万世享报之理。既有其理则必有其气之运于无穷者矣。
澌散之不久矣。圣人之生。钟毓于千古之元气者。则其死也亦当有英爽之不遽泯者矣。其聚散之久近。当视人品之高下。而其所未散。亦自是馀气之屈伸者。非有头面肢体。如释氏之冥府诸鬼也。沉香之臭似矣。而松脂之结而为珀则太涉乎物之矣。圣人生禀得许多气魄。参赞得天地之化。声教衣被乎万生。功德覆冒于千古。则其光灵赫赫。固当与天地之气。流通无间。而有万世享报之理。既有其理则必有其气之运于无穷者矣。圣人之知来。与谶纬术数之学异云云。
圣人之知来。推理以通微也。术家之知来。鍊气以神奸也。至如今日雷明日雹。后世有某人王某人侯之类。则圣人固不求知。亦不能知。
程子于太极妙旨。易传成书。尝秘之不发。朱子于图解也启蒙也。详说而遍告之。程子之于濂溪,横渠,康节。未见其有传习切偲之勤。而朱子则于延平,南轩,东莱。周旋讲明。不一而足。
风气有显晦。故教法亦有详略。随时之道。不得不尔也。自夫庖牺画卦而以至尧舜传心。文王演易。箕子陈范。孔子之撰十翼定礼乐修春秋。曾子子思之述学庸。孟子之谈仁义道性善。盖世愈下而教愈详也。不可以此而疑其法门之不同也。二程天姿甚纯。其受学于濂溪。想其一拨便解。而若其居敬躬行之实。则只自去到得。不烦师友之助。其与康节,横渠。亦多有周旋讲磨之益。而不屑屑于象数也。朱子则天姿虽高。而早岁学禅。不无陷溺。刚猛有馀而醇正不及于二程。又要包罗得天下大小大事。故须用十倍之功。须赖师友之助。耐辛耐苦。铢积寸集而得之。此其姿地之适然。亦岂法门之有不同耶。
朱子书与知旧门人往还者却多。而呈于延平者少。此亦可疑。
朱子二十四岁。将赴同安任。始见延平。自是奔走吏事。五年而罢归。二十九岁正月。再见延平。仍又监岳庙被召旨。不遑暇逸。其后亦尝再三至延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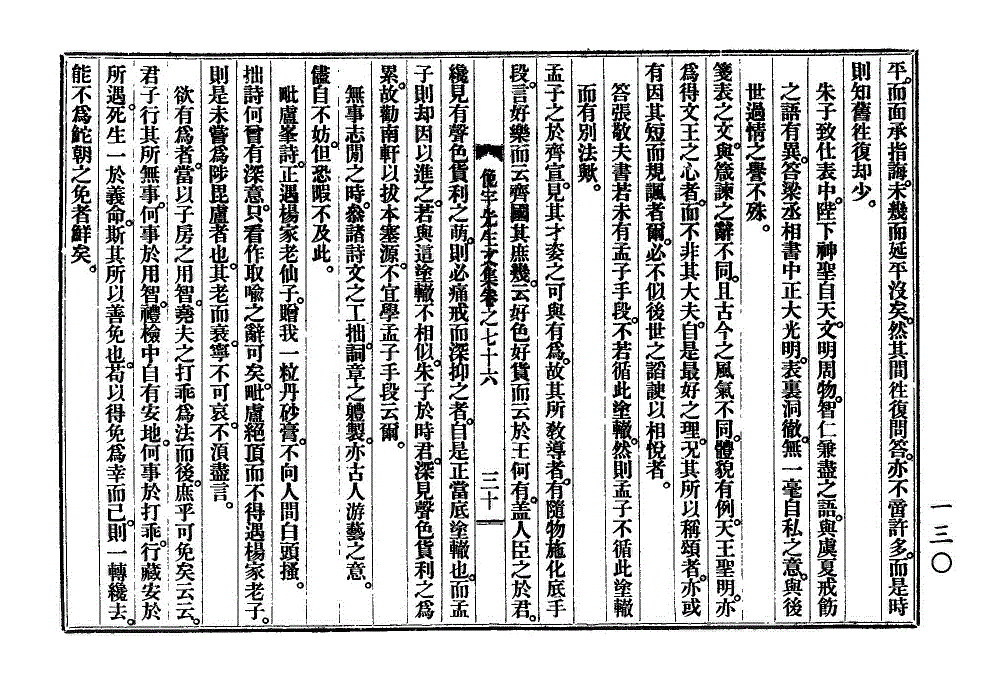 平。而面承指诲。未几而延平没矣。然其间往复问答。亦不啻许多。而是时则知旧往复却少。
平。而面承指诲。未几而延平没矣。然其间往复问答。亦不啻许多。而是时则知旧往复却少。朱子致仕表中。陛下神圣自天。文明周物。智仁兼尽之语。与虞夏戒饬之语有异。答梁丞相书中正大光明。表里洞彻。无一毫自私之意。与后世过情之誉不殊。
笺表之文。与箴谏之辞不同。且古今之风气不同。体貌有例。天王圣明。亦为得文王之心者。而不非其大夫。自是最好之理。况其所以称颂者。亦或有因其短而规讽者尔。必不似后世之谄谀以相悦者。
答张敬夫书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循此涂辙。然则孟子不循此涂辙而有别法欤。
孟子之于齐宣。见其才姿之可与有为。故其所教导者。有随物施化底手段。言好乐而云齐国其庶几。云好色好货而云于王何有。盖人臣之于君。才见有声色货利之萌。则必痛戒而深抑之者。自是正当底涂辙也。而孟子则却因以进之。若与这涂辙不相似。朱子于时君。深见声色货利之为累。故劝南轩以拔本塞源。不宜学孟子手段云尔。
无事志閒之时。参诸诗文之工拙。词章之体制。亦古人游艺之意。
尽自不妨。但恐暇不及此。
毗卢峰诗。正遇杨家老仙子。赠我一粒丹砂膏。不向人间白头搔。
拙诗何曾有深意。只看作取喻之辞可矣。毗卢绝顶而不得遇杨家老子。则是未尝为陟毗卢者也。其老而衰。宁不可哀。不须尽言。
欲有为者。当以子房之用智。尧夫之打乖为法而后。庶乎可免矣云云。
君子行其所无事。何事于用智。礼检中自有安地。何事于打乖。行藏安于所遇。死生一于义命。斯其所以善免也。苟以得免为幸而已。则一转才去。能不为鮀朝之免者鲜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六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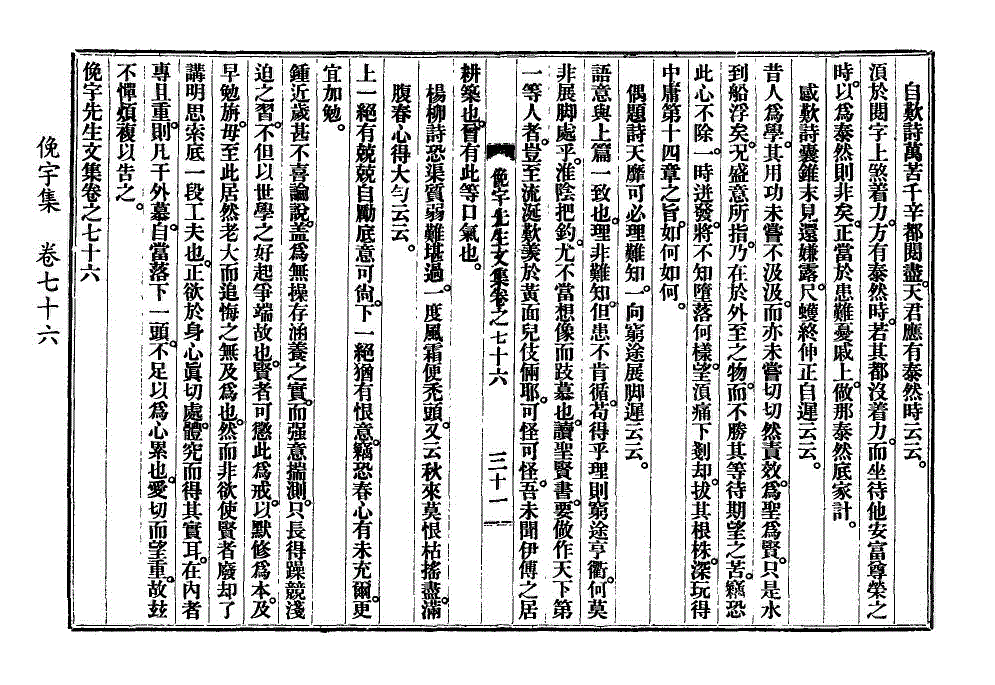 自叹诗万苦千辛都阅尽。天君应有泰然时云云。
自叹诗万苦千辛都阅尽。天君应有泰然时云云。须于阅字上煞着力。方有泰然时。若其都没着力。而坐待他安富尊荣之时。以为泰然则非矣。正当于患难忧戚上。做那泰然底家计。
感叹诗囊锥末见还嫌露。尺蠖终伸正自迟云云。
昔人为学。其用功未尝不汲汲。而亦未尝切切然责效。为圣为贤。只是水到船浮矣。况盛意所指。乃在于外至之物。而不胜其等待期望之苦。窃恐此心不除。一时迸发。将不知堕落何样。望须痛下刬却。拔其根株。深玩得中庸第十四章之旨。如何如何。
偶题诗天靡可必理难知。一向穷途展脚迟云云。
语意与上篇一致也。理非难知。但患不肯循。苟得乎理则穷途亨衢。何莫非展脚处乎。淮阴把钓。尤不当想像而跂慕也。读圣贤书。要做作天下第一等人者。岂至流涎叹羡于黄面儿伎俩耶。可怪可怪。吾未闻伊傅之居耕筑也。曾有此等口气也。
杨柳诗恐渠质弱难堪过。一度风霜便秃头。又云秋来莫恨枯摇尽。满腹春心得大匀云云。
上一绝有兢兢自励底意可尚。下一绝犹有恨意。窃恐春心有未充尔。更宜加勉。
钟近岁甚不喜论说。盖为无操存涵养之实。而强意揣测。只长得躁竞浅迫之习。不但以世学之好起争端故也。贤者可惩此为戒。以默修为本。及早勉旃。毋至此居然老大而追悔之无及为也。然而非欲使贤者废却了讲明思索底一段工夫也。正欲于身心真切处。体究而得其实耳。在内者专且重。则凡干外慕。自当落下一头。不足以为心累也。爱切而望重。故玆不惮烦复以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