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书
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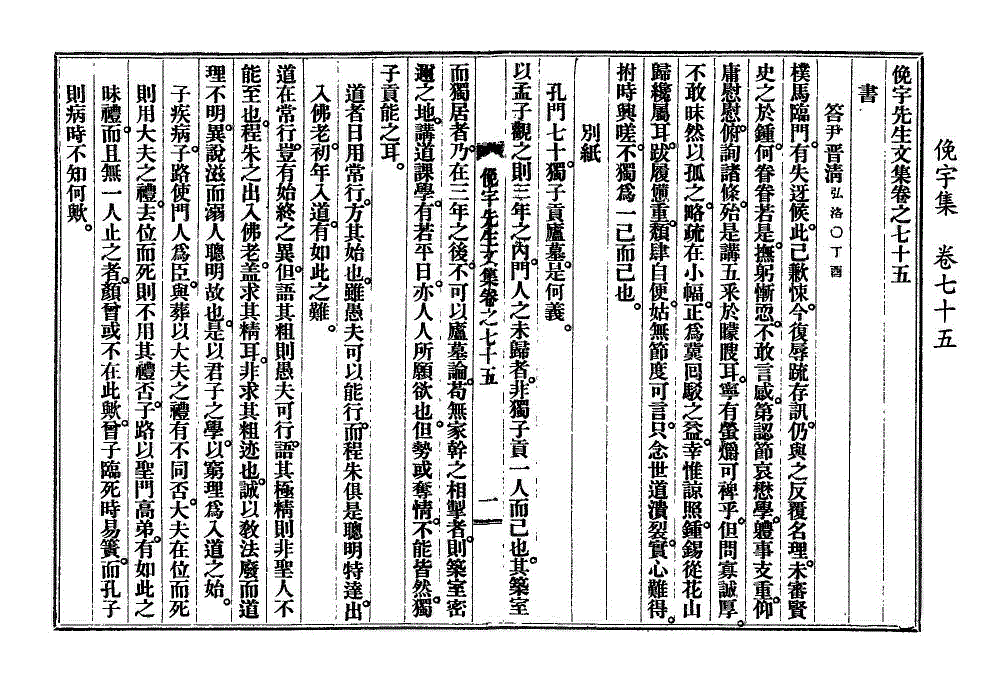 答尹晋清(弘洛○丁酉)
答尹晋清(弘洛○丁酉)朴马临门。有失迓候。此已歉悚。今复辱疏存讯。仍与之反覆名理。未审贤史之于钟。何眷眷若是。抚躬惭恧。不敢言感。第认节哀懋学。体事支重。仰庸慰慰。俯询诸条。殆是讲五采于矇瞍耳。宁有萤爝可裨乎。但问寡诚厚。不敢昧然以孤之。略疏在小幅。正为冀回驳之益。幸惟谅照。钟锡从花山归才属耳。跋履惫重。颓肆自便。姑无节度可言。只念世道溃裂。实心难得。拊时兴嗟。不独为一己而已也。
别纸
孔门七十。独子贡庐墓。是何义。
以孟子观之则三年之内。门人之未归者。非独子贡一人而已也。其筑室而独居者。乃在三年之后。不可以庐墓论。苟无家干之相掣者。则筑室密迩之地。讲道课学。有若平日。亦人人所愿欲也。但势或夺情。不能皆然。独子贡能之耳。
道者日用常行。方其始也。虽愚夫可以能行。而程朱俱是聪明特达。出入佛老。初年入道。有如此之难。
道在常行。岂有始终之异。但语其粗则愚夫可行。语其极精则非圣人不能至也。程朱之出入佛老。盖求其精耳。非求其粗迹也。诚以教法废而道理不明。异说滋而溺人聪明故也。是以君子之学。以穷理为入道之始。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与葬以大夫之礼有不同否。大夫在位而死则用大夫之礼。去位而死则不用其礼否。子路以圣门高弟。有如此之昧礼。而且无一人止之者。颜曾或不在此欤。曾子临死时易箦。而孔子则病时不知何欤。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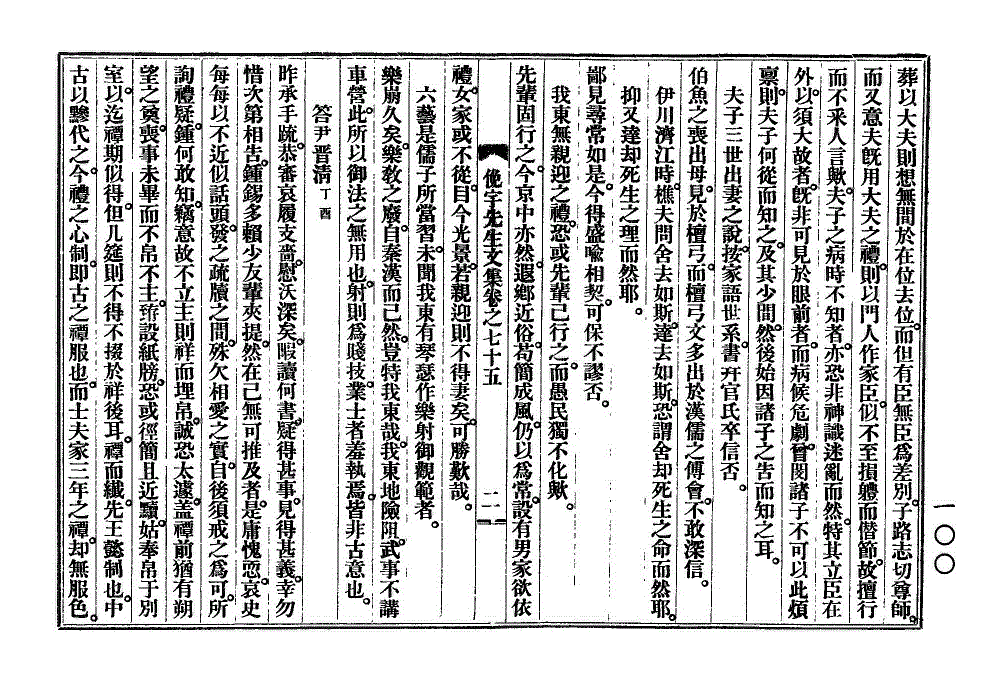 葬以大夫则想无间于在位去位。而但有臣无臣为差别。子路志切尊师。而又意夫既用大夫之礼。则以门人作家臣。似不至损体而僭节。故擅行而不采人言欤。夫子之病时不知者。亦恐非神识迷乱而然。特其立臣在外。以须大故者。既非可见于眼前者。而病候危剧。曾闵诸子不可以此烦禀。则夫子何从而知之。及其少间。然后始因诸子之告而知之耳。
葬以大夫则想无间于在位去位。而但有臣无臣为差别。子路志切尊师。而又意夫既用大夫之礼。则以门人作家臣。似不至损体而僭节。故擅行而不采人言欤。夫子之病时不知者。亦恐非神识迷乱而然。特其立臣在外。以须大故者。既非可见于眼前者。而病候危剧。曾闵诸子不可以此烦禀。则夫子何从而知之。及其少间。然后始因诸子之告而知之耳。夫子三世出妻之说。按家语世系。书幵官氏卒信否。
伯鱼之丧出母。见于檀弓。而檀弓文多出于汉儒之傅会。不敢深信。
伊川济江时。樵夫问舍去如斯。达去如斯。恐谓舍却死生之命而然耶。抑又达却死生之理而然耶。
鄙见寻常如是。今得盛喻相契。可保不谬否。
我东无亲迎之礼。恐或先辈已行之。而愚民独不化欤。
先辈固行之。今京中亦然。遐乡近俗。苟简成风。仍以为常。设有男家欲依礼。女家或不从。目今光景。若亲迎则不得妻矣。可胜叹哉。
六艺是儒子所当习。未闻我东有琴瑟作乐射御观范者。
乐崩久矣。乐教之废。自秦汉而已然。岂特我东哉。我东地险阻。武事不讲车营。此所以御法之无用也。射则为贱技。业士者羞执焉。皆非古意也。
答尹晋清(丁酉)
昨承手疏。恭审哀履支啬。慰沃深矣。暇读何书。疑得甚事。见得甚义。幸勿惜次第相告。钟锡多赖少友辈夹提。然在己无可推及者。是庸愧恧。哀史每每以不近似话头。发之疏牍之间。殊欠相爱之实。自后须戒之为可。所询礼疑。钟何敢知。窃意故不立主则祥而埋帛。诚恐太遽。盖禫前犹有朔望之奠。丧事未毕而不帛不主。臶设纸榜。恐或径简且近黩。姑奉帛于别室。以迄禫期似得。但几筵则不得不掇于祥后耳。禫而纤。先王懿制也。中古以黪代之。今礼之心制。即古之禫服也。而士夫家三年之禫。却无服色。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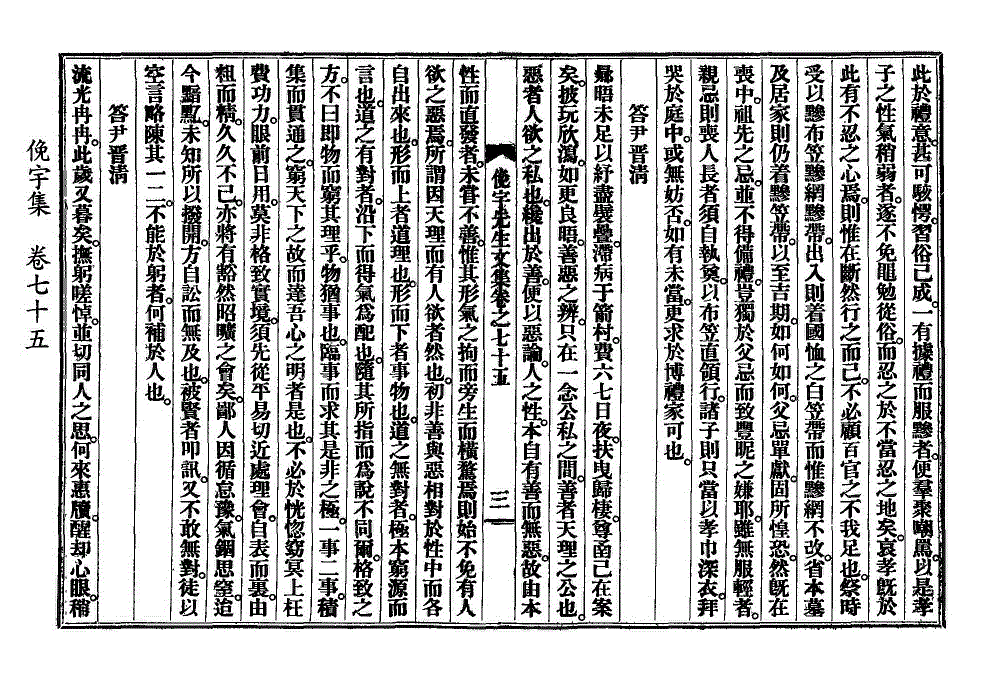 此于礼意。甚可骇愕。习俗已成。一有据礼而服黪者。便群聚嘲骂。以是孝子之性气稍弱者。遂不免黾勉从俗。而忍之于不当忍之地矣。哀孝既于此有不忍之心焉。则惟在断然行之而已。不必顾百官之不我足也。祭时受以黪布笠黪网黪带。出入则着国恤之白笠带而惟黪网不改。省本墓及居家则仍着黪笠带。以至吉期。如何如何。父忌单献。固所惶恐。然既在丧中。祖先之忌。并不得备礼。岂独于父忌而致丰昵之嫌耶。虽无服轻者。亲忌则丧人长者须自执奠。以布笠直领行。诸子则只当以孝巾深衣。拜哭于庭中。或无妨否。如有未当。更求于博礼家可也。
此于礼意。甚可骇愕。习俗已成。一有据礼而服黪者。便群聚嘲骂。以是孝子之性气稍弱者。遂不免黾勉从俗。而忍之于不当忍之地矣。哀孝既于此有不忍之心焉。则惟在断然行之而已。不必顾百官之不我足也。祭时受以黪布笠黪网黪带。出入则着国恤之白笠带而惟黪网不改。省本墓及居家则仍着黪笠带。以至吉期。如何如何。父忌单献。固所惶恐。然既在丧中。祖先之忌。并不得备礼。岂独于父忌而致丰昵之嫌耶。虽无服轻者。亲忌则丧人长者须自执奠。以布笠直领行。诸子则只当以孝巾深衣。拜哭于庭中。或无妨否。如有未当。更求于博礼家可也。答尹晋清
向晤未足以纾尽襞叠。滞病于箭村。费六七日夜。扶曳归栖。尊函已在案矣。披玩欣泻。如更良晤。善恶之辨。只在一念公私之间。善者天理之公也。恶者人欲之私也。才出于善。便以恶论。人之性。本自有善而无恶。故由本性而直发者。未尝不善。惟其形气之拘而旁生而横骛焉则始不免有人欲之恶焉。所谓因天理而有人欲者然也。初非善与恶相对于性中而各自出来也。形而上者道理也。形而下者事物也。道之无对者。极本穷源而言也。道之有对者。沿下而得气为配也。随其所指而为说不同尔。格致之方。不曰即物而穷其理乎。物犹事也。临事而求其是非之极。一事二事。积集而贯通之。穷天下之故而达吾心之明者是也。不必于恍惚窈冥上枉费功力。眼前日用。莫非格致实境。须先从平易切近处理会。自表而里。由粗而精。久久不已。亦将有豁然昭旷之会矣。鄙人因循怠豫。气锢思窒。迨今黯䵝。未知所以拨开。方自讼而无及也。被贤者叩讯。又不敢无对。徒以空言略陈其一二。不能于躬者。何补于人也。
答尹晋清
流光冉冉。此岁又暮矣。抚躬嗟悼。并切同人之思。何来惠牍。醒却心眼。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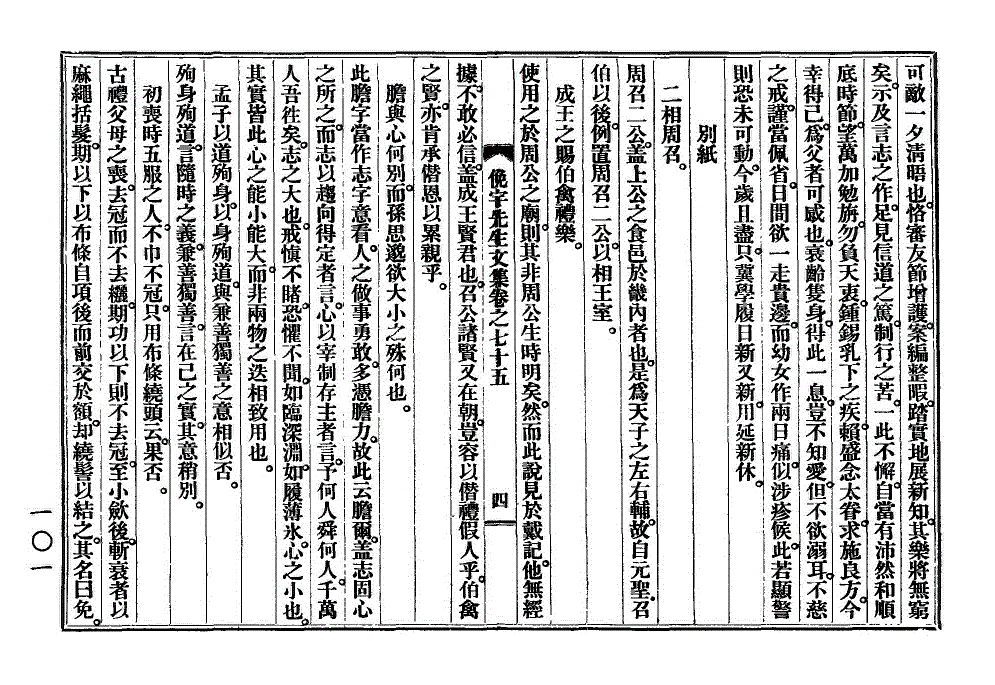 可敌一夕清晤也。恪审友节增护。案编整暇。踏实地展新知。其乐将无穷矣。示及言志之作。足见信道之笃。制行之苦。一此不懈。自当有沛然和顺底时节。望万加勉旃。勿负天衷。钟锡乳下之疾。赖盛念太眷。求施良方。今幸得已。为父者可感也。衰龄只身。得此一息。岂不知爱。但不欲溺耳。不慈之戒。谨当佩省。日间欲一走贵边。而幼女作两日痛。似涉疹候。此若显警则恐未可动。今岁且尽。只冀学履日新又新。用延新休。
可敌一夕清晤也。恪审友节增护。案编整暇。踏实地展新知。其乐将无穷矣。示及言志之作。足见信道之笃。制行之苦。一此不懈。自当有沛然和顺底时节。望万加勉旃。勿负天衷。钟锡乳下之疾。赖盛念太眷。求施良方。今幸得已。为父者可感也。衰龄只身。得此一息。岂不知爱。但不欲溺耳。不慈之戒。谨当佩省。日间欲一走贵边。而幼女作两日痛。似涉疹候。此若显警则恐未可动。今岁且尽。只冀学履日新又新。用延新休。别纸
二相周召。
周召二公。盖上公之食邑于畿内者也。是为天子之左右辅。故自元圣,召伯以后。例置周召二公。以相王室。
成王之赐伯禽礼乐。
使用之于周公之庙。则其非周公生时明矣。然而此说见于戴记。他无经据。不敢必信。盖成王贤君也。召公诸贤又在朝。岂容以僭礼假人乎。伯禽之贤。亦肯承僭恩以累亲乎。
胆与心何别。而孙思邈欲大小之殊何也。
此胆字当作志字意看。人之做事勇敢。多凭胆力。故此云胆尔。盖志固心之所之。而志以趋向得定者言。心以宰制存主者言。予何人舜何人。千万人吾往矣。志之大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之小也。其实皆此心之能小能大。而非两物之迭相致用也。
孟子以道殉身。以身殉道。与兼善独善之意相似否。
殉身殉道。言随时之义。兼善独善。言在己之实。其意稍别。
初丧时五服之人。不巾不冠。只用布条绕头云。果否。
古礼父母之丧。去冠而不去纚。期功以下则不去冠。至小敛后。斩衰者以麻绳括发。期以下以布条自项后而前交于额。却绕髻以结之。其名曰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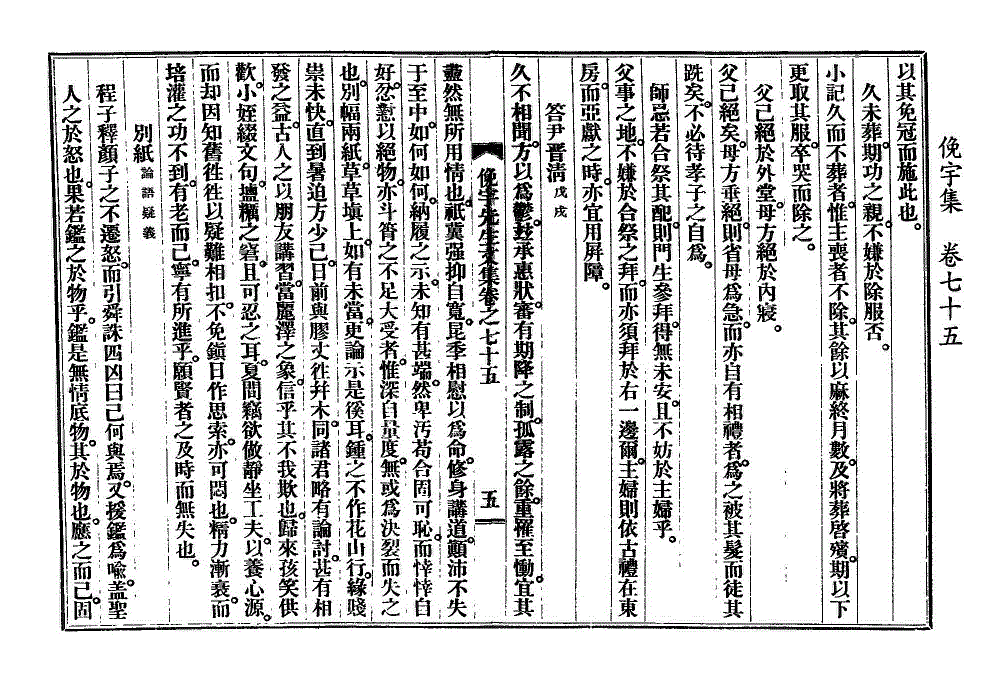 以其免冠而施此也。
以其免冠而施此也。久未葬。期功之亲。不嫌于除服否。
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其馀以麻终月数。及将葬启殡。期以下更取其服。卒哭而除之。
父已绝于外堂。母方绝于内寝。
父已绝矣。母方垂绝。则省母为急。而亦自有相礼者。为之被其发而徒其跣矣。不必待孝子之自为。
师忌若合祭其配。则门生参拜。得无未安。且不妨于主妇乎。
父事之地。不嫌于合祭之拜。而亦须拜于右一边尔。主妇则依古礼在东房。而亚献之时。亦宜用屏障。
答尹晋清(戊戌)
久不相闻。方以为郁。玆承惠状。审有期降之制。孤露之馀。重罹至恸。宜其衋然无所用情也。祇冀强抑自宽。昆季相慰以为命。修身讲道。颠沛不失于至中。如何如何。纳履之示。未知有甚端。然卑污苟合固可耻。而悻悻自好。忿怼以绝物。亦斗筲之不足大受者。惟深自量度。无或为决裂而失之也。别幅两纸。草草填上。如有未当。更论示是徯耳。钟之不作花山行。缘贱祟未快。直到暑迫方少已。日前与胶丈往并木。同诸君略有论讨。甚有相发之益。古人之以朋友讲习。当丽泽之象。信乎其不我欺也。归来孩笑供欢。小侄缀文句。盐粝之窘。且可忍之耳。夏间窃欲做静坐工夫。以养心源。而却因知旧往往以疑难相扣。不免镇日作思索。亦可闷也。精力渐衰。而培灌之功不到。有老而已。宁有所进乎。愿贤者之及时而无失也。
别纸(论语疑义)
程子释颜子之不迁怒。而引舜诛四凶曰己何与焉。又援鉴为喻。盖圣人之于怒也。果若鉴之于物乎。鉴是无情底物。其于物也。应之而已。固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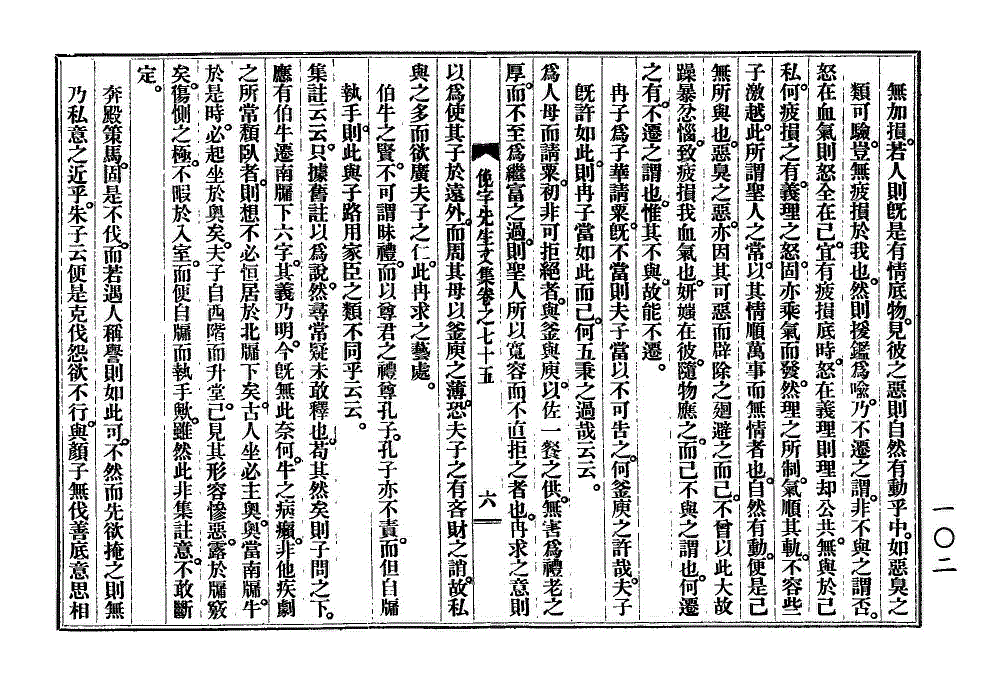 无加损。若人则既是有情底物。见彼之恶则自然有动乎中。如恶臭之类可验。岂无疲损于我也。然则援鉴为喻。乃不迁之谓。非不与之谓否。
无加损。若人则既是有情底物。见彼之恶则自然有动乎中。如恶臭之类可验。岂无疲损于我也。然则援鉴为喻。乃不迁之谓。非不与之谓否。怒在血气则怒全在己。宜有疲损底时。怒在义理则理却公共。无与于己私。何疲损之有。义理之怒。固亦乘气而发。然理之所制。气顺其轨。不容些子激越。此所谓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者也。自然有动。便是已无所与也。恶臭之恶。亦因其可恶而辟除之回避之而已。不曾以此大故躁暴忿恼。致疲损我血气也。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已不与之谓也。何迁之有。不迁之谓也。惟其不与。故能不迁。
冉子为子华请粟。既不当则夫子当以不可告之。何釜庾之许哉。夫子既许如此。则冉子当如此而已。何五秉之过哉云云。
为人母而请粟。初非可拒绝者。与釜与庾。以佐一餐之供。无害为礼老之厚。而不至为继富之过。则圣人所以宽容而不直拒之者也。冉求之意则以为使其子于远外。而周其母以釜庾之薄。恐夫子之有吝财之诮。故私与之多而欲广夫子之仁。此冉求之艺处。
伯牛之贤。不可谓昧礼。而以尊君之礼尊孔子。孔子亦不责。而但自牖执手。则此与子路用家臣之类不同乎云云。
集注云云。只据旧注以为说。然寻常疑未敢释也。苟其然矣则子问之下。应有伯牛迁南牖下六字。其义乃明。今既无此奈何。牛之病癞。非他疾剧之所常颓卧者。则想不必恒居于北牖下矣。古人坐必主奥。奥当南牖。牛于是时。必起坐于奥矣。夫子自西阶而升堂。已见其形容惨恶。露于牖窍矣。伤恻之极。不暇于入室。而便自牖而执手欤。虽然此非集注意。不敢断定。
奔殿策马。固是不伐。而若遇人称誉则如此可。不然而先欲掩之则无乃私意之近乎。朱子云便是克伐怨欲不行。与颜子无伐善底意思相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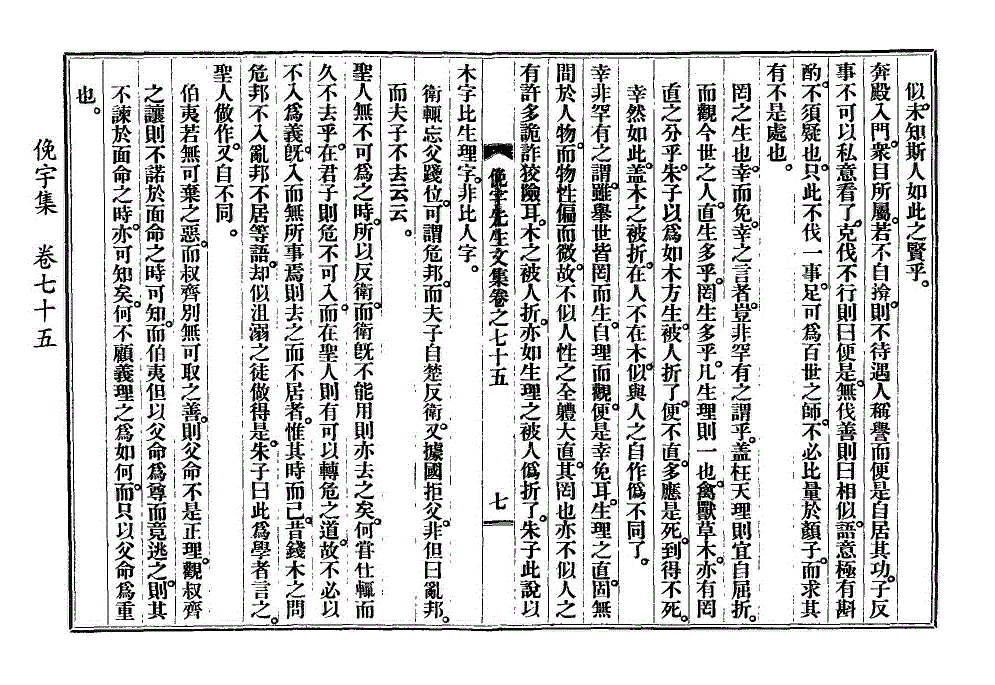 似。未知斯人如此之贤乎。
似。未知斯人如此之贤乎。奔殿入门。众目所属。若不自掩。则不待遇人称誉而便是自居其功。子反事不可以私意看了。克伐不行则曰便是。无伐善则曰相似。语意极有斟酌。不须疑也。只此不伐一事。足可为百世之师。不必比量于颜子。而求其有不是处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幸之言者。岂非罕有之谓乎。盖枉天理则宜自屈折。而观今世之人。直生多乎。罔生多乎。凡生理则一也。禽兽草木。亦有罔直之分乎。朱子以为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应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盖木之被折。在人不在木。似与人之自作伪不同了。
幸非罕有之谓。虽举世皆罔而生。自理而观。便是幸免耳。生理之直。固无间于人物。而物性偏而微。故不似人性之全体大直。其罔也亦不似人之有许多诡诈狡险耳。木之被人折。亦如生理之被人伪折了。朱子此说以木字比生理字。非比人字。
卫辄忘父践位。可谓危邦。而夫子自楚反卫。又据国拒父。非但曰乱邦而夫子不去云云。
圣人无不可为之时。所以反卫。而卫既不能用则亦去之矣。何尝仕辄而久不去乎。在君子则危不可入。而在圣人则有可以转危之道。故不必以不入为义。既入而无所事焉则去之而不居者。惟其时而已。昔钱木之问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等语。却似沮溺之徒做得是。朱子曰此为学者言之。圣人做作。又自不同。
伯夷若无可弃之恶。而叔齐别无可取之善。则父命不是正理。观叔齐之让则不诺于面命之时可知。而伯夷但以父命为尊而竟逃之。则其不谏于面命之时。亦可知矣。何不顾义理之为如何。而只以父命为重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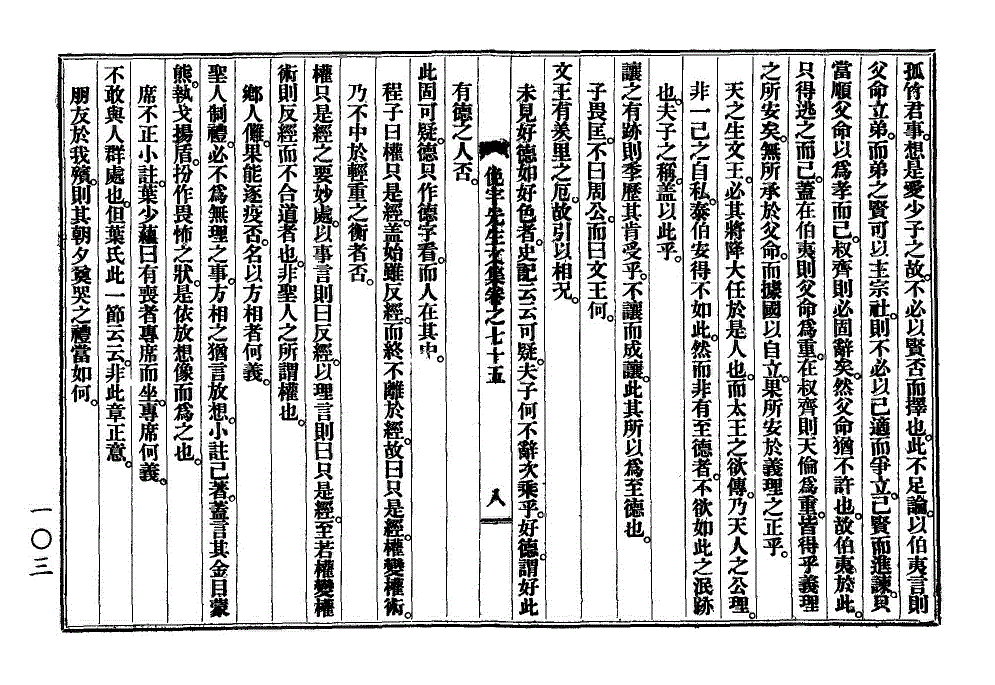 孤竹君事。想是爱少子之故。不必以贤否而择也。此不足论。以伯夷言则父命立弟。而弟之贤可以主宗社。则不必以己适而争立。己贤而进谏。只当顺父命以为孝而已。叔齐则必固辞矣。然父命犹不许也。故伯夷于此。只得逃之而已。盖在伯夷则父命为重。在叔齐则天伦为重。皆得乎义理之所安矣。无所承于父命。而据国以自立。果所安于义理之正乎。
孤竹君事。想是爱少子之故。不必以贤否而择也。此不足论。以伯夷言则父命立弟。而弟之贤可以主宗社。则不必以己适而争立。己贤而进谏。只当顺父命以为孝而已。叔齐则必固辞矣。然父命犹不许也。故伯夷于此。只得逃之而已。盖在伯夷则父命为重。在叔齐则天伦为重。皆得乎义理之所安矣。无所承于父命。而据国以自立。果所安于义理之正乎。天之生文王。必其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而太王之欲传。乃天人之公理。非一己之自私。泰伯安得不如此。然而非有至德者。不欲如此之泯迹也。夫子之称。盖以此乎。
让之有迹则季历其肯受乎。不让而成让。此其所以为至德也。
子畏匡。不曰周公。而曰文王何。
文王有羑里之厄。故引以相况。
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史记云云可疑。夫子何不辞次乘乎。好德。谓好此有德之人否。
此固可疑。德只作德字看。而人在其中。
程子曰权只是经。盖始虽反经。而终不离于经。故曰只是经。权变权术。乃不中于轻重之衡者否。
权只是经之要妙处。以事言则曰反经。以理言则曰只是经。至若权变权术则反经而不合道者也。非圣人之所谓权也。
乡人傩。果能逐疫否。名以方相者何义。
圣人制礼。必不为无理之事。方相之犹言放想。小注已著。盖言其金目蒙熊。执戈扬盾。扮作畏怖之状。是依放想像而为之也。
席不正小注。叶少蕴曰有丧者专席而坐。专席何义。
不敢与人群处也。但叶氏此一节云云。非此章正意。
朋友于我殡。则其朝夕奠哭之礼当如何。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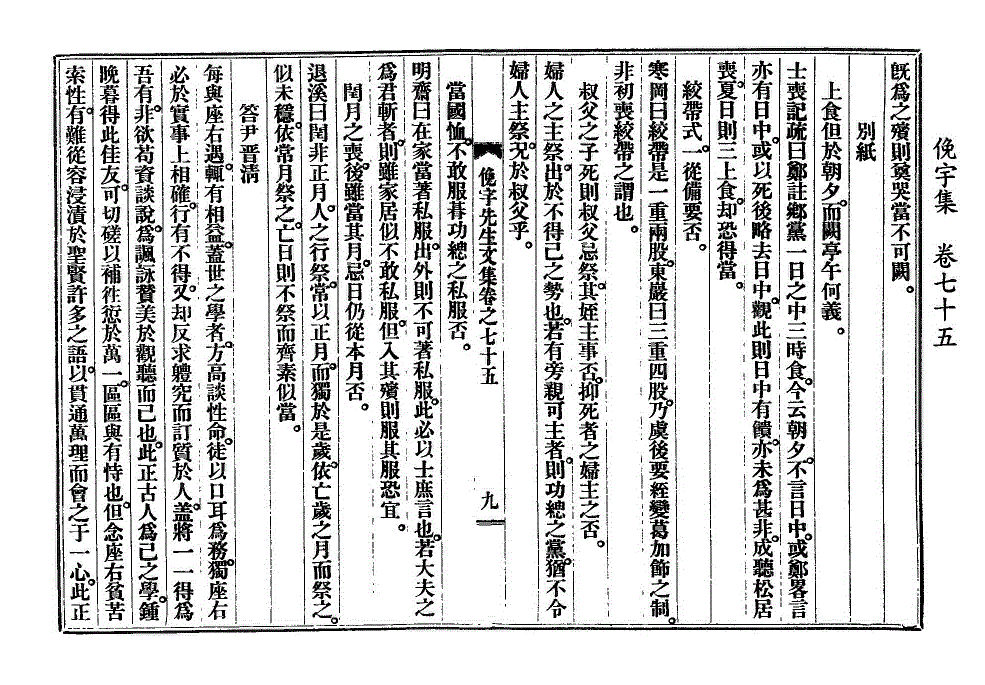 既为之殡则奠哭当不可阙。
既为之殡则奠哭当不可阙。别纸
上食但于朝夕。而阙亭午何义。
士丧记疏曰郑注乡党一日之中三时食。今云朝夕。不言日中。或郑略言亦有日中。或以死后略去日中。观此则日中有馈。亦未为甚非。成听松居丧。夏日则三上食。却恐得当。
绞带式。一从备要否。
寒冈曰绞带是一重两股。东岩曰三重四股。乃虞后要绖变葛加饰之制。非初丧绞带之谓也。
叔父之子死则叔父忌祭。其侄主事否。抑死者之妇主之否。
妇人之主祭。出于不得已之势也。若有旁亲可主者。则功缌之党。犹不令妇人主祭。况于叔父乎。
当国恤。不敢服期功缌之私服否。
明斋曰在家当著私服。出外则不可著私服。此必以士庶言也。若大夫之为君斩者。则虽家居似不敢私服。但入其殡则服其服恐宜。
闰月之丧。后虽当其月。忌日仍从本月否。
退溪曰闰非正月。人之行祭。常以正月。而独于是岁。依亡岁之月而祭之。似未稳。依常月祭之。亡日则不祭而齐素似当。
答尹晋清
每与座右遇。辄有相益。盖世之学者。方高谈性命。徒以口耳为务。独座右必于实事上相确。行有不得。又却反求体究而订质于人。盖将一一得为吾有。非欲苟资谈说。为讽咏赞美于观听而已也。此正古人为己之学。钟晚暮得此佳友。可切磋以补往愆于万一。区区与有恃也。但念座右贫苦索性。有难从容浸渍于圣贤许多之语。以贯通万理而会之于一心。此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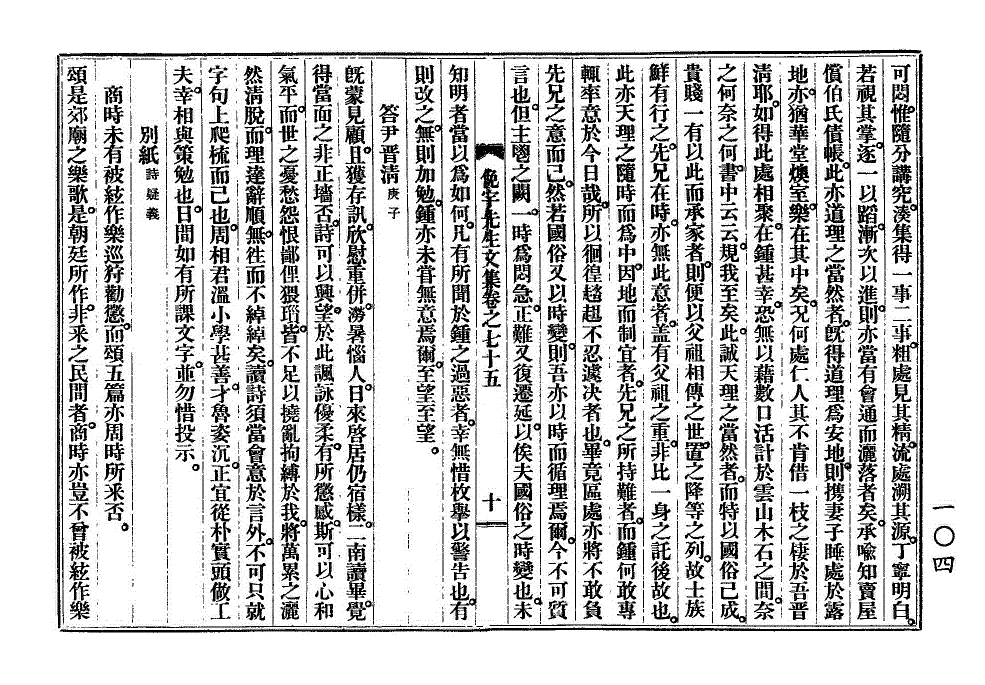 可闷。惟随分讲究。凑集得一事二事。粗处见其精。流处溯其源。丁宁明白。若视其掌。逐一以蹈。渐次以进。则亦当有会通而洒落者矣。承喻知卖屋偿伯氏债帐。此亦道理之当然者。既得道理为安地。则携妻子睡处于露地。亦犹华堂燠室。乐在其中矣。况何处仁人其不肯借一枝之栖于吾晋清耶。如得此处相聚。在钟甚幸。恐无以藉数口活计于云山木石之间。奈之何奈之何。书中云云。规我至矣。此诚天理之当然者。而特以国俗已成。贵贱一有以此而承家者。则便以父祖相传之世。置之降等之列。故士族鲜有行之。先兄在时。亦无此意者。盖有父祖之重。非比一身之托后故也。此亦天理之随时而为中。因地而制宜者。先兄之所持难者。而钟何敢专辄率意于今日哉。所以徊徨趑趄不忍遽决者也。毕竟区处亦将不敢负先兄之意而已。然若国俗又以时变。则吾亦以时而循理焉尔。今不可质言也。但主鬯之阙。一时为闷急。正难又复迁延。以俟夫国俗之时变也。未知明者当以为如何。凡有所闻于钟之过恶者。幸无惜枚举以警告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钟亦未尝无意焉尔。至望至望。
可闷。惟随分讲究。凑集得一事二事。粗处见其精。流处溯其源。丁宁明白。若视其掌。逐一以蹈。渐次以进。则亦当有会通而洒落者矣。承喻知卖屋偿伯氏债帐。此亦道理之当然者。既得道理为安地。则携妻子睡处于露地。亦犹华堂燠室。乐在其中矣。况何处仁人其不肯借一枝之栖于吾晋清耶。如得此处相聚。在钟甚幸。恐无以藉数口活计于云山木石之间。奈之何奈之何。书中云云。规我至矣。此诚天理之当然者。而特以国俗已成。贵贱一有以此而承家者。则便以父祖相传之世。置之降等之列。故士族鲜有行之。先兄在时。亦无此意者。盖有父祖之重。非比一身之托后故也。此亦天理之随时而为中。因地而制宜者。先兄之所持难者。而钟何敢专辄率意于今日哉。所以徊徨趑趄不忍遽决者也。毕竟区处亦将不敢负先兄之意而已。然若国俗又以时变。则吾亦以时而循理焉尔。今不可质言也。但主鬯之阙。一时为闷急。正难又复迁延。以俟夫国俗之时变也。未知明者当以为如何。凡有所闻于钟之过恶者。幸无惜枚举以警告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钟亦未尝无意焉尔。至望至望。答尹晋清(庚子)
既蒙见顾。且获存讯。欣慰重并。涝暑恼人。日来启居仍宿样。二南读毕。觉得当面之非正墙否。诗可以兴。望于此讽咏优柔。有所惩感。斯可以心和气平。而世之忧愁怨恨鄙俚猥琐。皆不足以挠乱拘缚于我。将万累之洒然清脱。而理达辞顺。无往而不绰绰矣。读诗须当会意于言外。不可只就字句上爬梳而已也。周相君温小学甚善。才鲁姿沉。正宜从朴实头做工夫。幸相与策勉也。日间如有所课文字。并勿惜投示。
别纸(诗疑义)
商时未有被弦作乐巡狩劝惩。而颂五篇亦周时所采否。
颂是郊庙之乐歌。是朝廷所作。非采之民间者。商时亦岂不曾被弦作乐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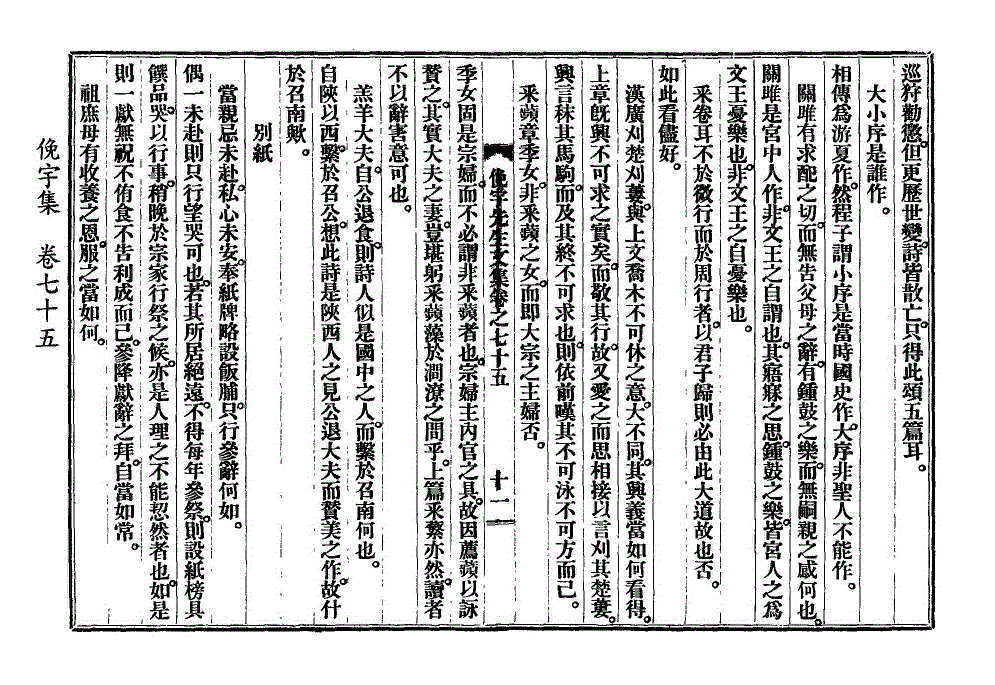 巡狩劝惩。但更历世变。诗皆散亡。只得此颂五篇耳。
巡狩劝惩。但更历世变。诗皆散亡。只得此颂五篇耳。大小序是谁作。
相传为游夏作。然程子谓小序是当时国史作。大序非圣人不能作。
关雎有求配之切。而无告父母之辞。有钟鼓之乐。而无嗣亲之感何也。
关雎是宫中人作。非文王之自谓也。其寤寐之思。钟鼓之乐。皆宫人之为文王忧乐也。非文王之自忧乐也。
采卷耳不于微行而于周行者。以君子归则必由此大道故也否。
如此看尽好。
汉广刈楚刈蒌。与上文乔木不可休之意。大不同。其兴义当如何看得。
上章既兴不可求之实矣。而敬其行。故又爱之而思相接以言刈其楚蒌。兴言秣其马驹。而及其终不可求也。则依前叹其不可泳不可方而已。
采蘋章季女。非采蘋之女。而即大宗之主妇否。
季女固是宗妇。而不必谓非采蘋者也。宗妇主内官之具。故因荐蘋以咏赞之。其实大夫之妻。岂堪躬采蘋藻于涧潦之间乎。上篇采蘩亦然。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
羔羊大夫。自公退食。则诗人似是国中之人。而系于召南何也。
自陕以西。系于召公。想此诗是陕西人之见公退大夫而赞美之作。故什于召南欤。
别纸
当亲忌未赴。私心未安。奉纸牌略设饭脯。只行参辞何如。
偶一未赴则只行望哭可也。若其所居绝远。不得每年参祭。则设纸榜具馔品。哭以行事。稍晚于宗家行祭之候。亦是人理之不能恝然者也。如是则一献无祝不侑食不告利成而已。参降献辞之拜。自当如常。
祖庶母有收养之恩。服之当如何。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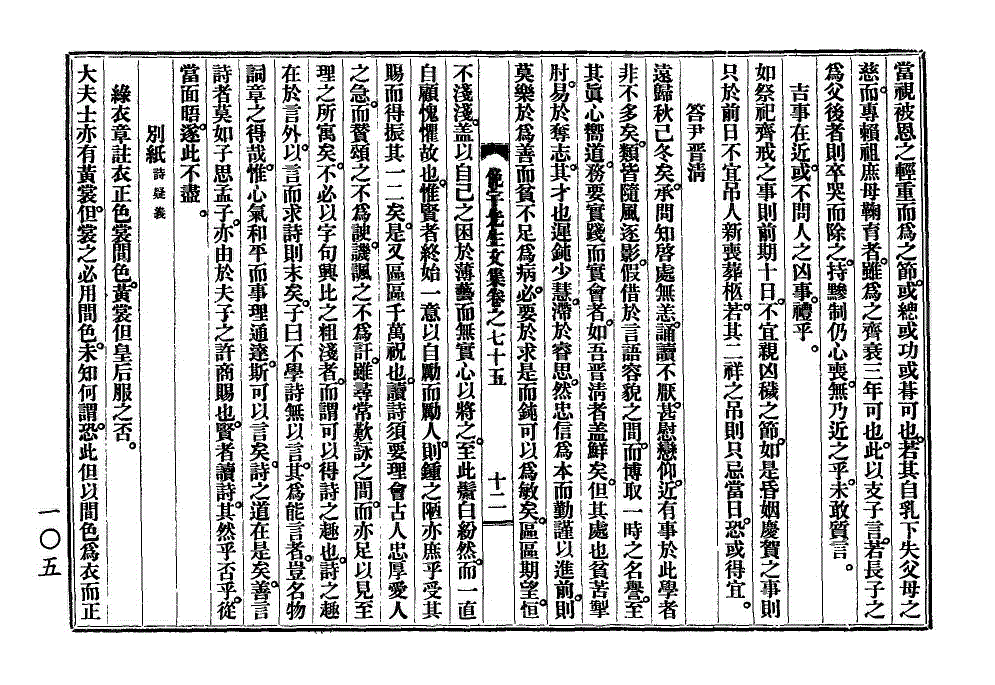 当视被恩之轻重而为之节。或缌或功或期可也。若其自乳下失父母之慈。而专赖祖庶母鞠育者。虽为之齐衰三年可也。此以支子言。若长子之为父后者则卒哭而除之。持黪制仍心丧。无乃近之乎。末敢质言。
当视被恩之轻重而为之节。或缌或功或期可也。若其自乳下失父母之慈。而专赖祖庶母鞠育者。虽为之齐衰三年可也。此以支子言。若长子之为父后者则卒哭而除之。持黪制仍心丧。无乃近之乎。末敢质言。吉事在近。或不问人之凶事。礼乎。
如祭祀齐戒之事则前期十日。不宜亲凶秽之节。如是昏姻庆贺之事则只于前日不宜吊人新丧葬柩。若其二祥之吊则只忌当日。恐或得宜。
答尹晋清
远归秋已冬矣。承问知启处无恙。诵读不厌。甚慰恋仰。近有事于此学者非不多矣。类皆随风逐影。假借于言语容貌之间。而博取一时之名誉。至其真心向道。务要实践而实会者。如吾晋清者盖鲜矣。但其处也贫苦掣肘。易于夺志。其才也迟钝少慧。滞于睿思。然忠信为本而勤谨以进前。则莫乐于为善而贫不足为病。必要于求是而钝可以为敏矣。区区期望。恒不浅浅。盖以自己之困于薄艺而无实心以将之。至此鬓白纷然。而一直自顾愧惧故也。惟贤者终始一意以自励而励人。则钟之陋亦庶乎受其赐而得振其一二矣。是又区区千万祝也。读诗须要理会古人忠厚爱人之急。而赞颂之不为谀。讥讽之不为讦。虽寻常叹咏之间。而亦足以见至理之所寓矣。不必以字句兴比之粗浅者。而谓可以得诗之趣也。诗之趣在于言外。以言而求诗则末矣。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其为能言者。岂名物词章之得哉。惟心气和平而事理通达。斯可以言矣。诗之道在是矣。善言诗者莫如子思孟子。亦由于夫子之许商赐也。贤者读诗。其然乎否乎。从当面晤。遂此不尽。
别纸(诗疑义)
绿衣章注衣正色裳间色。黄裳但皇后服之否。
大夫士亦有黄裳。但裳之必用间色。未知何谓。恐此但以间色为衣而正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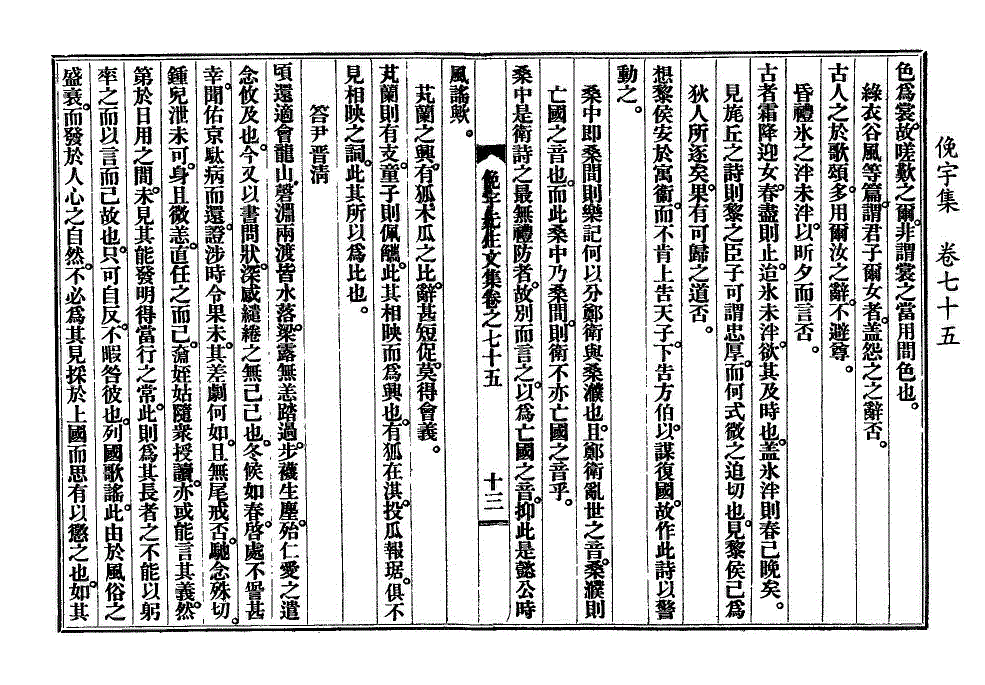 色为裳。故嗟叹之尔。非谓裳之当用间色也。
色为裳。故嗟叹之尔。非谓裳之当用间色也。绿衣谷风等篇。谓君子尔女者。盖怨之之辞否。
古人之于歌颂。多用尔汝之辞。不避尊。
昏礼冰之泮未泮。以昕夕而言否。
古者霜降迎女。春尽则止。迨冰未泮。欲其及时也。盖冰泮则春已晚矣。
见旄丘之诗则黎之臣子可谓忠厚。而何式微之迫切也。见黎侯已为狄人所逐矣。果有可归之道否。
想黎侯安于寓卫。而不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谋复国。故作此诗以警动之。
桑中即桑间则乐记何以分郑卫与桑濮也。且郑卫乱世之音。桑濮则亡国之音也。而此桑中乃桑间。则卫不亦亡国之音乎。
桑中是卫诗之最无礼防者。故别而言之。以为亡国之音。抑此是懿公时风谣欤。
芄兰之兴。有狐,木瓜之比。辞甚短促。莫得会义。
芃兰则有支。童子则佩觿。此其相映而为兴也。有狐在淇。投瓜报琚。俱不见相映之词。此其所以为比也。
答尹晋清
顷还适会龙山,磬渊两渡皆水落。梁露无恙踏过。步袜生尘。殆仁爱之遣念攸及也。今又以书问状。深感缱绻之无已已也。冬候如春。启处不愆甚幸。闻佑京驮病而还。證涉时令果未。其差剧何如。且无尾戒否。驰念殊切。钟儿泄未可。身且微恙。直任之而已。奫侄姑随众授读。亦或能言其义。然第于日用之间。未见其能发明得当行之常。此则为其长者之不能以躬率之而以言而已故也。只可自反。不暇咎彼也。列国歌谣。此由于风俗之盛衰。而发于人心之自然。不必为其见采于上国而思有以惩之也。如其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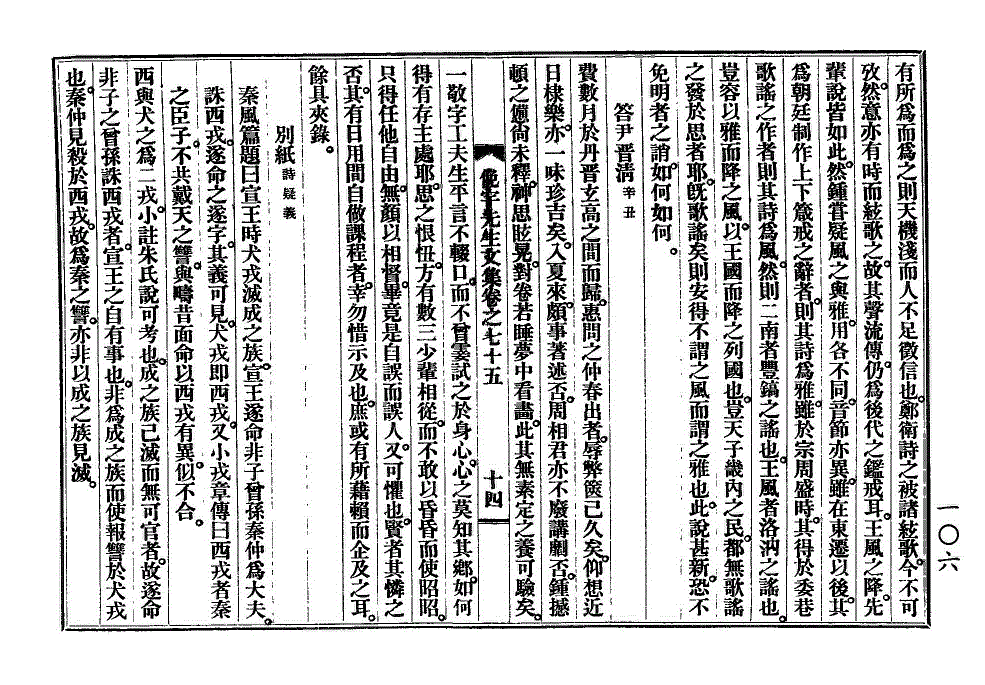 有所为而为之则天机浅而人不足徵信也。郑卫诗之被诸弦歌。今不可考。然意亦有时而弦歌之。故其声流传。仍为后代之鉴戒耳。王风之降。先辈说皆如此。然钟尝疑风之与雅。用各不同。音节亦异。虽在东迁以后。其为朝廷制作上下箴戒之辞者。则其诗为雅。虽于宗周盛时。其得于委巷歌谣之作者则其诗为风。然则二南者丰镐之谣也。王风者洛汭之谣也。岂容以雅而降之风。以王国而降之列国也。岂天子畿内之民。都无歌谣之发于思者耶。既歌谣矣则安得不谓之风而谓之雅也。此说甚新。恐不免明者之诮。如何如何。
有所为而为之则天机浅而人不足徵信也。郑卫诗之被诸弦歌。今不可考。然意亦有时而弦歌之。故其声流传。仍为后代之鉴戒耳。王风之降。先辈说皆如此。然钟尝疑风之与雅。用各不同。音节亦异。虽在东迁以后。其为朝廷制作上下箴戒之辞者。则其诗为雅。虽于宗周盛时。其得于委巷歌谣之作者则其诗为风。然则二南者丰镐之谣也。王风者洛汭之谣也。岂容以雅而降之风。以王国而降之列国也。岂天子畿内之民。都无歌谣之发于思者耶。既歌谣矣则安得不谓之风而谓之雅也。此说甚新。恐不免明者之诮。如何如何。答尹晋清(辛丑)
费数月于丹晋玄高之间而归。惠问之仲春出者。辱弊箧已久矣。仰想近日棣乐。亦一味珍吉矣。入夏来。颇事著述否。周相君亦不废讲劘否。钟撼顿之惫尚未释。神思眩晃。对卷若睡梦中看画。此其无素定之养可验矣。一敬字工夫生平言不辍口。而不曾霎试之于身心。心之莫知其乡。如何得有存主处耶。思之恨忸。方有数三少辈相从。而不敢以昏昏而使昭昭。只得任他自由。无颜以相督。毕竟是自误而误人。又可惧也。贤者其怜之否。其有日用间自做课程者。幸勿惜示及也。庶或有所藉赖而企及之耳。馀具夹录。
别纸(诗疑义)
秦风篇题曰宣王时犬戎灭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遂命之遂字。其义可见。犬戎即西戎。又小戎章传曰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雠。与畴昔面命以西戎有异。似不合。
西与犬之为二戎。小注朱氏说可考也。成之族已灭而无可官者。故遂命非子之曾孙诛西戎者。宣王之自有事也。非为成之族而使报雠于犬戎也。秦仲见杀于西戎。故为秦之雠。亦非以成之族见灭。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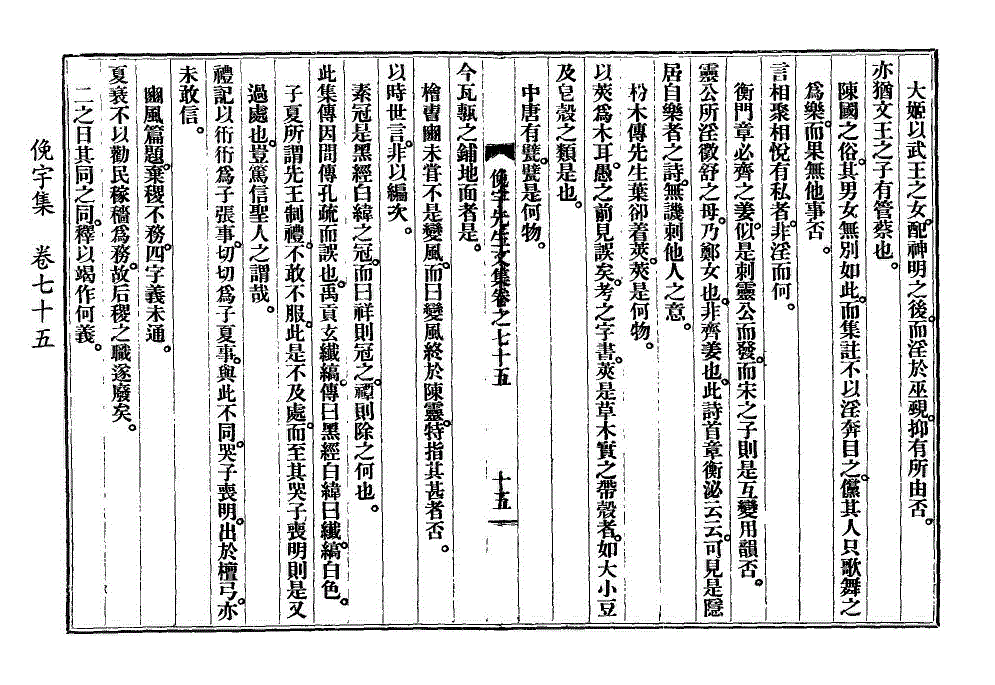 大姬以武王之女。配神明之后。而淫于巫觋。抑有所由否。
大姬以武王之女。配神明之后。而淫于巫觋。抑有所由否。亦犹文王之子有管蔡也。
陈国之俗。其男女无别如此。而集注不以淫奔目之。傥其人只歌舞之为乐。而果无他事否。
言相聚相悦有私者。非淫而何。
衡门章必齐之姜。似是刺灵公而发。而宋之子则是互变用韵否。
灵公所淫徵舒之母。乃郑女也。非齐姜也。此诗首章衡泌云云。可见是隐居自乐者之诗。无讥刺他人之意。
枌木传先生叶却着荚。荚是何物。
以荚为木耳。愚之前见误矣。考之字书。荚是草木实之带壳者。如大小豆及皂壳之类是也。
中唐有甓。甓是何物。
今瓦砖之铺地面者是。
桧曹豳未尝不是变风。而曰变风终于陈灵。特指其甚者否。
以时世言。非以编次。
素冠是黑经白纬之冠。而曰祥则冠之。禫则除之何也。
此集传因间传孔疏而误也。禹贡玄纤缟。传曰黑经白纬曰纤。缟白色。
子夏所谓先王制礼。不敢不服。此是不及处。而至其哭子丧明则是又过处也。岂笃信圣人之谓哉。
礼记以衎衎为子张事。切切为子夏事。与此不同。哭子丧明。出于檀弓。亦未敢信。
豳风篇题。弃稷不务。四字义未通。
夏衰不以劝民稼穑为务。故后稷之职遂废矣。
二之日其同之同。释以竭作何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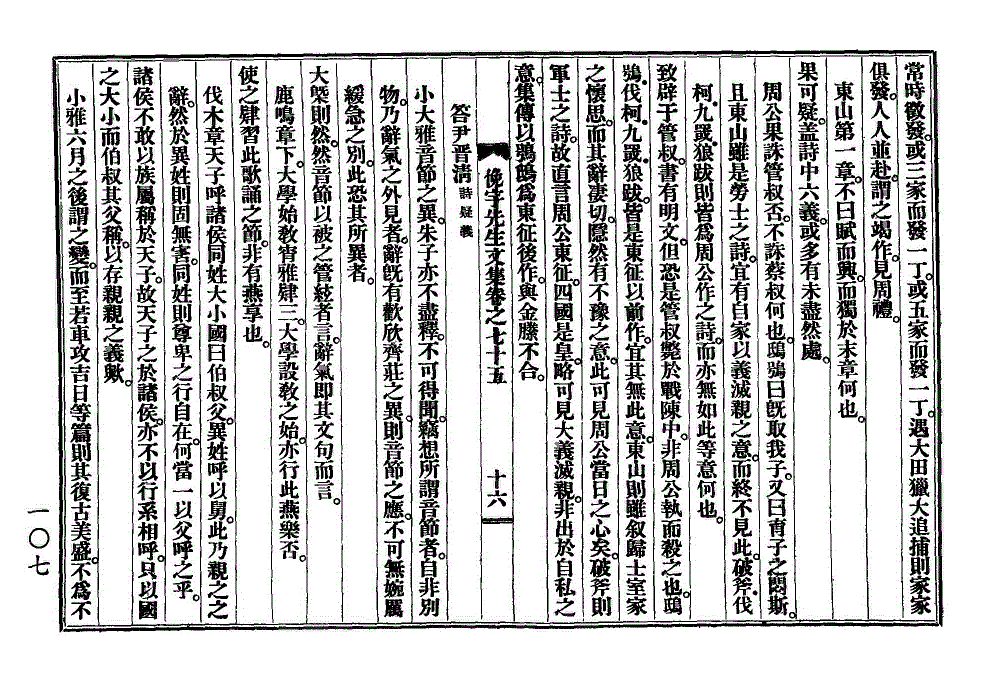 常时徵发。或三家而发一丁。或五家而发一丁。遇大田猎大追捕则家家俱发。人人并赴。谓之竭作。见周礼。
常时徵发。或三家而发一丁。或五家而发一丁。遇大田猎大追捕则家家俱发。人人并赴。谓之竭作。见周礼。东山第一章。不曰赋而兴。而独于末章何也。
果可疑。盖诗中六义。或多有未尽然处。
周公果诛管叔否。不诛蔡叔何也。鸱鸮曰既取我子。又曰育子之闷斯。且东山虽是劳士之诗。宜有自家以义灭亲之意。而终不见此。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则皆为周公作之诗。而亦无如此等意何也。
致辟于管叔。书有明文。但恐是管叔毙于战陈中。非周公执而杀之也。鸱鸮,伐柯,九罭,狼跋。皆是东征以前作。宜其无此意。东山则虽叙归士室家之怀思。而其辞凄切。隐然有不豫之意。此可见周公当日之心矣。破斧则军士之诗。故直言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略可见大义灭亲。非出于自私之意。集传以鸮鸱为东征后作。与金縢不合。
答尹晋清(诗疑义)
小大雅音节之异。朱子亦不尽释。不可得闻。窃想所谓音节者。自非别物。乃辞气之外见者。辞既有欢欣齐庄之异。则音节之应。不可无婉厉缓急之别。此恐其所异者。
大槩则然。然音节以被之管弦者言。辞气即其文句而言。
鹿鸣章下。大学始教宵雅肄三。大学设教之始。亦行此燕乐否。
使之肄习此歌诵之节。非有燕享也。
伐木章天子呼诸侯同姓大小国曰伯叔父。异姓呼以舅。此乃亲之之辞。然于异姓则固无害。同姓则尊卑之行自在。何当一以父呼之乎。
诸侯不敢以族属称于天子。故天子之于诸侯。亦不以行系相呼。只以国之大小而伯叔其父称。以存亲亲之义欤。
小雅六月之后谓之变。而至若车攻吉日等篇则其复古美盛。不为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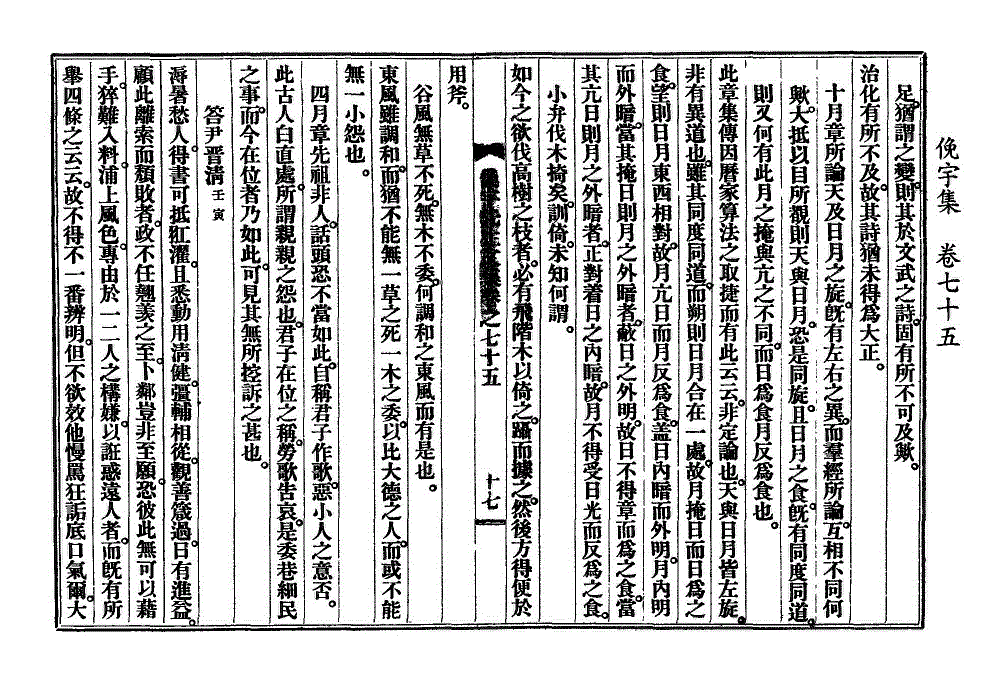 足。犹谓之变。则其于文武之诗。固有所不可及欤。
足。犹谓之变。则其于文武之诗。固有所不可及欤。治化有所不及。故其诗犹未得为大正。
十月章所论天及日月之旋。既有左右之异。而群经所论。互相不同何欤。大抵以目所睹则天与日月。恐是同旋。且日月之食。既有同度同道。则又何有此月之掩与亢之不同。而日为食月反为食也。
此章集传因历家算法之取捷而有此云云。非定论也。天与日月皆左旋。非有异道也。虽其同度同道。而朔则日月合在一处。故月掩日而日为之食。望则日月东西相对。故月亢日而月反为食。盖日内暗而外明。月内明而外暗。当其掩日则月之外暗者。蔽日之外明。故日不得章而为之食。当其亢日则月之外暗者。正对着日之内暗。故月不得受日光而反为之食。
小弁伐木掎矣。训倚。未知何谓。
如今之欲伐高树之枝者。必有飞阶木以倚之。蹑而据之。然后方得便于用斧。
谷风无草不死。无木不委。何调和之东风而有是也。
东风虽调和。而犹不能无一草之死一木之委。以比大德之人。而或不能无一小怨也。
四月章先祖非人。话头恐不当如此。自称君子作歌。恶小人之意否。
此古人白直处。所谓亲亲之怨也。君子在位之称。劳歌告哀。是委巷细民之事。而今在位者乃如此。可见其无所控诉之甚也。
答尹晋清(壬寅)
溽暑愁人。得书可抵羾濯。且悉动用清健。彊辅相从。观善箴过。日有进益。顾此离索而颓败者。政不任翘羡之至。卜邻岂非至愿。恐彼此无可以藉手。猝难入料。浦上风色。专由于一二人之构嫌。以诳惑远人者。而既有所举四条之云云。故不得不一番辨明。但不欲效他慢骂狂诟底口气尔。大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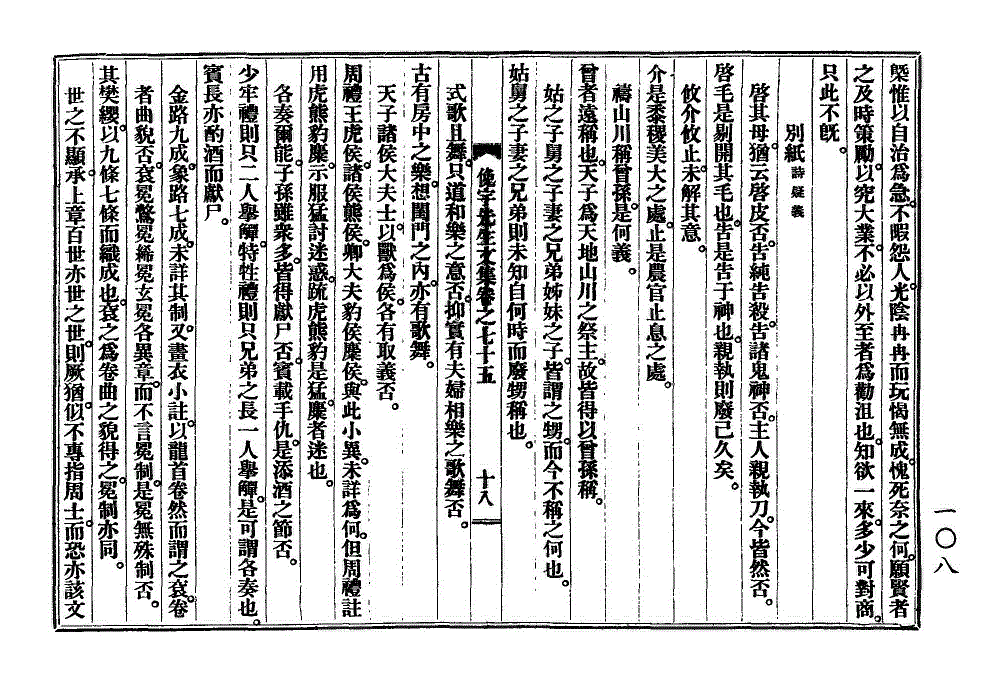 槩惟以自治为急。不暇怨人。光阴冉冉而玩愒无成。愧死奈之何。愿贤者之及时策励。以究大业。不必以外至者为劝沮也。知欲一来。多少可对商。只此不既。
槩惟以自治为急。不暇怨人。光阴冉冉而玩愒无成。愧死奈之何。愿贤者之及时策励。以究大业。不必以外至者为劝沮也。知欲一来。多少可对商。只此不既。别纸(诗疑义)
启其母(一作毛)。犹云启皮否。告纯告杀。告诸鬼神否。主人亲执刀。今皆然否。
启毛是剔开其毛也。告是告于神也。亲执则废已久矣。
攸介攸止。未解其意。
介是黍稷美大之处。止是农官止息之处。
祷山川称曾孙。是何义。
曾者远称也。天子为天地山川之祭主。故皆得以曾孙称。
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兄弟姊妹之子。皆谓之甥。而今不称之何也。
姑舅之子妻之兄弟则未知自何时而废甥称也。
式歌且舞。只道和乐之意否。抑实有夫妇相乐之歌舞否。
古有房中之乐。想闺门之内。亦有歌舞。
天子诸侯大夫士。以兽为侯。各有取义否。
周礼王虎侯。诸侯熊侯。卿大夫豹侯麋侯。与此小异。未详为何。但周礼注用虎熊豹麋。示服猛讨迷惑。疏虎熊豹是猛。麋者迷也。
各奏尔能。子孙虽众多。皆得献尸否。宾载手仇。是添酒之节否。
少牢礼则只二人举觯。特牲礼则只兄弟之长一人举觯。是可谓各奏也。宾长亦酌酒而献尸。
金路九成。象路七成。未详其制。又画衣小注。以龙首卷然而谓之衮。卷者曲貌否。衮冕鷩冕絺冕玄冕各异章。而不言冕制。是冕无殊制否。
其樊缨。以九条七条而织成也。衮之为卷曲之貌得之。冕制亦同。
世之不显。承上章百世亦世之世。则厥犹。似不专指周士。而恐亦该文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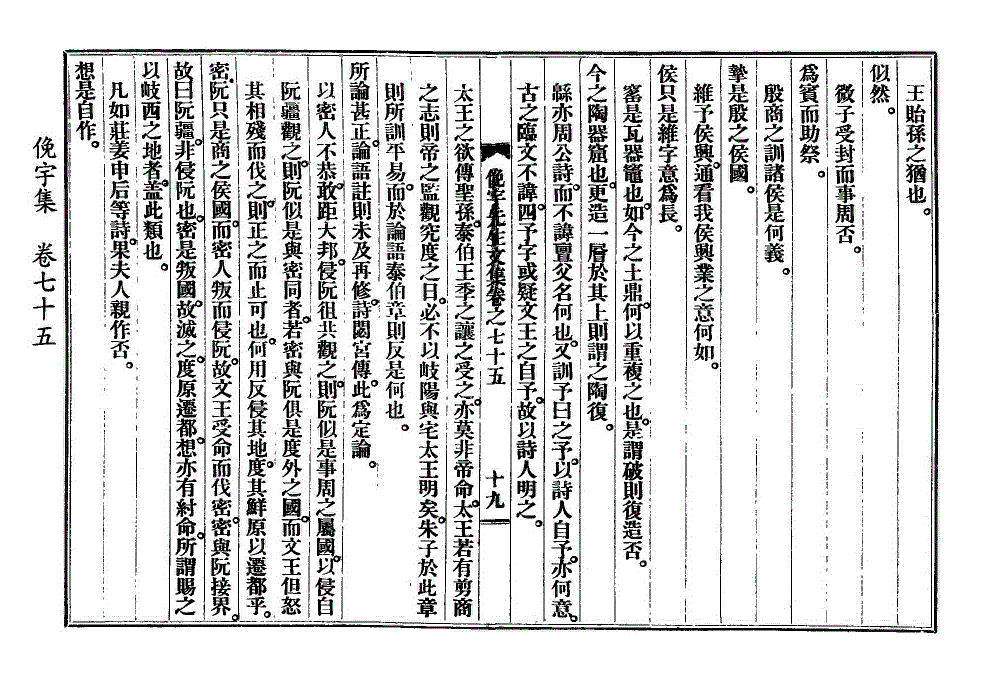 王贻孙之犹也。
王贻孙之犹也。似然。
微子受封而事周否。
为宾而助祭。
殷商之训诸侯是何义。
挚是殷之侯国。
维予侯兴。通看我侯兴业之意何如。
侯只是维字意为长。
窑是瓦器灶也。如今之土鼎。何以重复之也。是谓破则复造否。
今之陶器窟也。更造一层于其上则谓之陶复。
绵亦周公诗。而不讳亶父名何也。又训予曰之予。以诗人自予。亦何意。古之人临文不讳。四予字或疑文王之自予。故以诗人明之。
太王之欲传圣孙。泰伯王季之让之受之。亦莫非帝命。太王若有剪商之志则帝之监观究度之日。必不以岐阳与宅太王明矣。朱子于此章则所训平易。而于论语泰伯章则反是何也。
所论甚正。论语注则未及再修。诗閟宫传。此为定论。
以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观之。则阮似是事周之属国。以侵自阮疆观之。则阮似是与密同者。若密与阮俱是度外之国。而文王但怒其相残而伐之。则正之而止可也。何用反侵其地。度其鲜原以迁都乎。
密,阮只是商之侯国。而密人叛而侵阮。故文王受命而伐密。密与阮接界。故曰阮疆。非侵阮也。密是叛国。故灭之。度原迁都。想亦有纣命。所谓赐之以岐西之地者。盖此类也。
凡如庄姜申后等诗。果夫人亲作否。
想是自作。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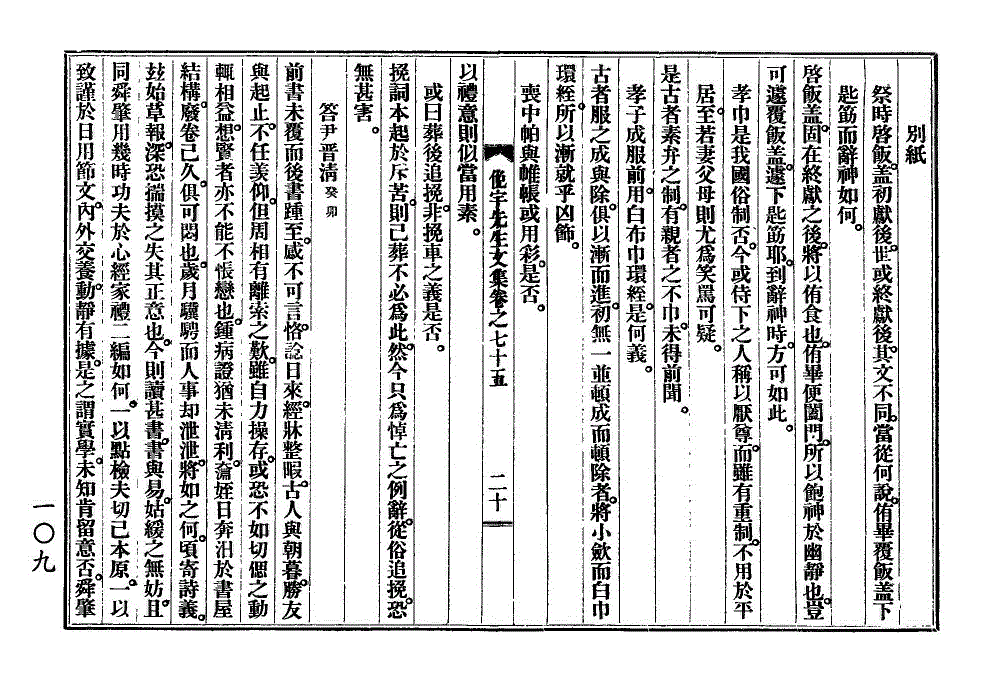 别纸
别纸祭时启饭。盖初献后。世或终献后。其文不同。当从何说。侑毕覆饭盖下匙箸而辞神如何。
启饭盖。固在终献之后。将以侑食也。侑毕便阖门。所以饱神于幽静也。岂可遽覆饭盖。遽下匙箸耶。到辞神时。方可如此。
孝巾是我国俗制否。今或侍下之人称以厌尊。而虽有重制。不用于平居。至若妻父母则尤为笑骂可疑。
是古者素弁之制。有亲者之不巾。未得前闻。
孝子成服前。用白布巾环绖。是何义。
古者服之成与除。俱以渐而进。初无一并顿成而顿除者。将小敛而白巾环绖。所以渐就乎凶饰。
丧中帕与帷帐或用彩。是否。
以礼意则似当用素。
或曰葬后追挽。非挽车之义是否。
挽词本起于斥苦。则已葬不必为此。然今只为悼亡之例辞。从俗追挽。恐无甚害。
答尹晋清(癸卯)
前书未覆而后书踵至。感不可言。恪谂日来。经床整暇。古人与朝暮。胜友与起止。不任羡仰。但周相有离索之叹。虽自力操存。或恐不如切偲之动辄相益。想贤者亦不能不怅恋也。钟病證犹未清利。奫侄日奔汩于书屋结构。废卷已久。俱可闷也。岁月骥骋而人事却泄泄。将如之何。顷寄诗义。玆始草报。深恐揣摸之失其正意也。今则读甚书。书与易。姑缓之无妨。且同舜肇用几时功夫于心经家礼二编如何。一以点检夫切己本原。一以致谨于日用节文。内外交养。动静有据。是之谓实学。未知肯留意否。舜肇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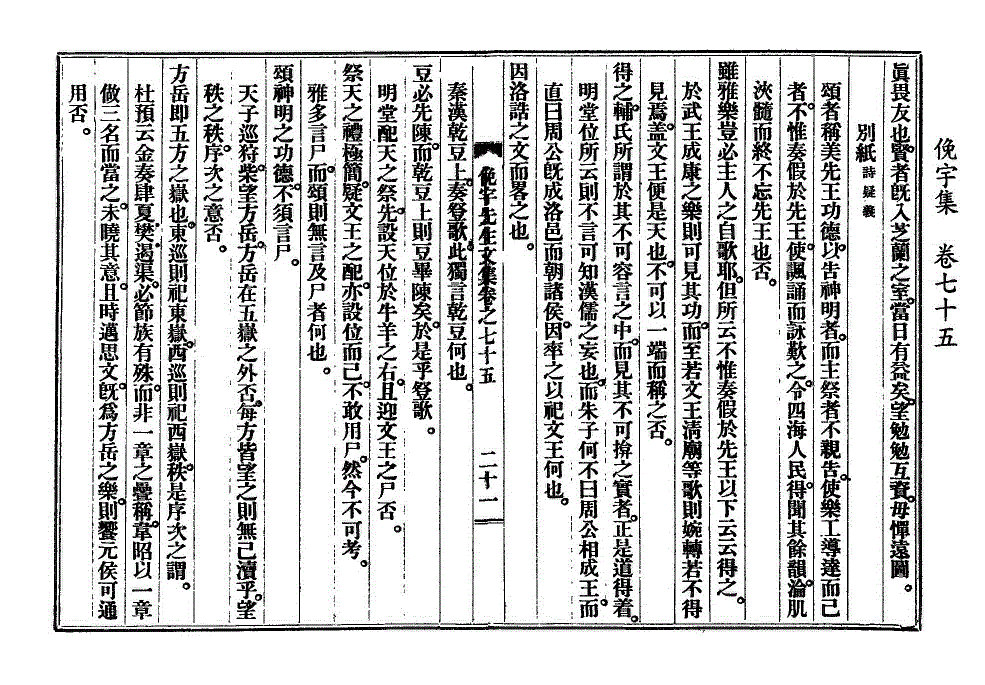 真畏友也。贤者既入芝兰之室。当日有益矣。望勉勉互资。毋惮远图。
真畏友也。贤者既入芝兰之室。当日有益矣。望勉勉互资。毋惮远图。别纸(诗疑义)
颂者称美先王功德。以告神明者。而主祭者不亲告。使乐工导达而已者。不惟奏假于先王。使讽诵而咏叹之。令四海人民。得闻其馀韵。沦肌浃髓而终不忘先王也否。
虽雅乐岂必主人之自歌耶。但所云不惟奏假于先王以下云云得之。
于武王成康之乐则可见其功。而至若文王清庙等歌则婉转若不得见焉。盖文王便是天也。不可以一端而称之否。
得之。辅氏所谓于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见其不可掩之实者。正是道得着。
明堂位所云则不言可知汉儒之妄也。而朱子何不曰周公相成王。而直曰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何也。
因洛诰之文而略之也。
秦汉乾豆上。奏登歌。此独言乾豆何也。
豆必先陈。而乾豆上则豆毕陈矣。于是乎登歌。
明堂配天之祭。先设天位于牛羊之右。且迎文王之尸否。
祭天之礼极简。疑文王之配。亦设位而已。不敢用尸。然今不可考。
雅多言尸。而颂则无言及尸者何也。
颂神明之功德。不须言尸。
天子巡狩。柴望方岳。方岳在五岳之外否。每方皆望之则无已渎乎。望秩之秩。序次之意否。
方岳即五方之岳也。东巡则祀东岳。西巡则祀西岳。秩是序次之谓。
杜预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必节族有殊。而非一章之叠称。韦昭以一章做三名而当之。未晓其意。且时迈思文。既为方岳之乐。则飨元侯可通用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0L 页
 韦说亦何尝以一章做三名耶。方岳之祀。因朝会诸侯。故祀飨通用。
韦说亦何尝以一章做三名耶。方岳之祀。因朝会诸侯。故祀飨通用。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一里当为九夫之地。而噫嘻注三十三里有奇。为万夫之地。小注百亩方百步。三夫为一里何也。
纵一里为三夫。横一里为三夫。纵横一里为方里。而三三为九夫。百步者三分里之一也。即一夫之地也。三其百步则乃一里三夫也。三十三里为九十九夫而有奇者。一夫之百步也。并为百夫纵横三十三里有奇。则百百为万夫。
访落,敬之,小毖等篇。告无告神之辞。似非正祭之乐。当何所用。
访落是朝庙之乐。而群臣因献戒则又以敬之答其意。而若告质于先王之前者也。小毖则是平管蔡后告庙之乐欤。不敢详。
成王赐伯禽礼乐。记说可疑。而诗有鲁颂。果以是否。论语八佾雍彻等篇。夫子只讥三家而止者。果讳之也否。且颂中必有祀周公之乐歌。而不可得见。则盖通用周颂否。鲁既曰颂。而因用风雅体何故。抑作者效之不得否。
记说果可疑。鲁之有颂。恐亦后世之失也。是以周公之庙无颂。而后世遂僭用周颂欤。因风雅体。想作者之效不得。且有颂祷之辞。其意自别故也。夫子之讥三家。为三家而言。言鲁僭则亦曰郊禘非礼。
牺尊何取义于牛也。
以牲用牺牛故欤。
盖田赋之制。考司马法。则方十里为一乘。侯封百里之制。则十井为一乘。而二制相左。窃以天子邦畿千里。出车万乘之例推之。则十井一乘似得。而朱子于孟子则曰地方百里出车千乘。此閟宫则曰三百十六里有奇何也。
司马法则并山林川泽不食之地而言。閟宫之传以此也。王制则断以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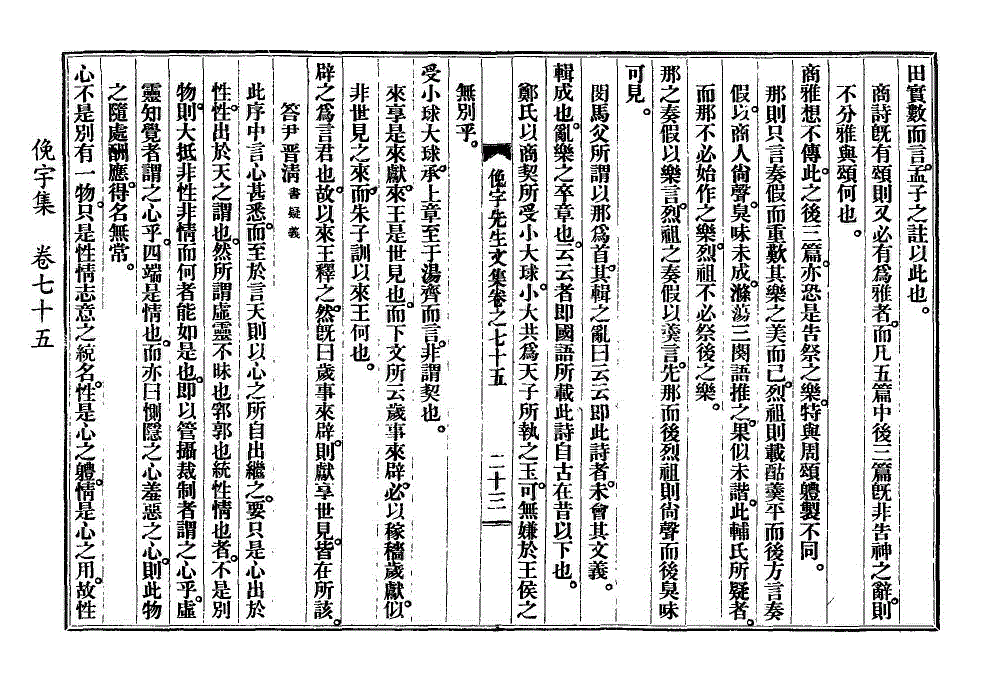 田实数而言。孟子之注以此也。
田实数而言。孟子之注以此也。商诗既有颂则又必有为雅者。而凡五篇中后三篇既非告神之辞。则不分雅与颂何也。
商雅想不传。此之后三篇。亦恐是告祭之乐。特与周颂体制不同。
那则只言奏假而重叹其乐之美而已。烈祖则载酤羹平而后方言奏假。以商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三阕语推之。果似未谐。此辅氏所疑者。而那不必始作之乐。烈祖不必祭后之乐。
那之奏假以乐言。烈祖之奏假以羹言。先那而后烈祖则尚声而后臭味可见。
闵马父所谓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云云即此诗者。未会其文义。
辑成也。乱乐之卒章也。云云者即国语所载此诗自古在昔以下也。
郑氏以商契所受小大球。小大共为天子所执之玉。可无嫌于王侯之无别乎。
受小球大球。承上章至于汤齐而言。非谓契也。
来享是来献。来王是世见也。而下文所云岁事来辟。必以稼穑岁献。似非世见之来。而朱子训以来王何也。
辟之为言君也。故以来王释之。然既曰岁事来辟。则献享世见。皆在所该。
答尹晋清(书疑义)
此序中言心甚悉。而至于言天则以心之所自出继之。要只是心出于性。性出于天之谓也。然所谓虚灵不昧也郛郭也统性情也者。不是别物。则大抵非性非情而何者能如是也。即以管摄裁制者谓之心乎。虚灵知觉者谓之心乎。四端是情也。而亦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则此物之随处酬应。得名无常。
心不是别有一物。只是性情志意之统名。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故性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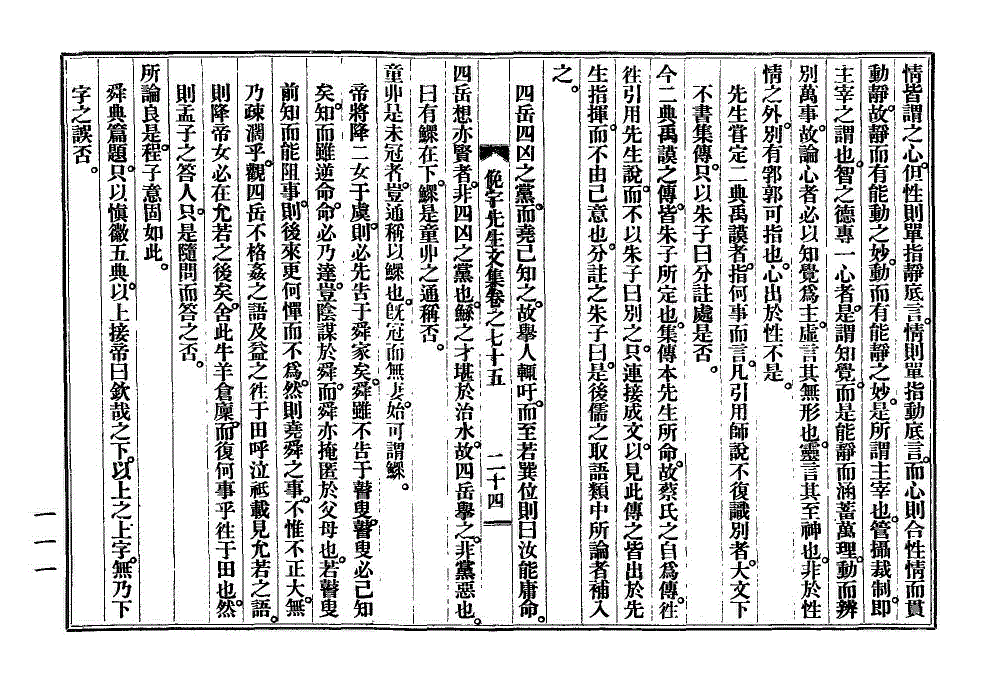 情皆谓之心。但性则单指静底言。情则单指动底言。而心则合性情而贯动静。故静而有能动之妙。动而有能静之妙。是所谓主宰也。管摄裁制。即主宰之谓也。智之德专一心者。是谓知觉。而是能静而涵蓄万理。动而辨别万事。故论心者必以知觉为主。虚言其无形也。灵言其至神也。非于性情之外。别有郛郭可指也。心出于性不是。
情皆谓之心。但性则单指静底言。情则单指动底言。而心则合性情而贯动静。故静而有能动之妙。动而有能静之妙。是所谓主宰也。管摄裁制。即主宰之谓也。智之德专一心者。是谓知觉。而是能静而涵蓄万理。动而辨别万事。故论心者必以知觉为主。虚言其无形也。灵言其至神也。非于性情之外。别有郛郭可指也。心出于性不是。先生尝定二典禹谟者。指何事而言。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者。大文下不书集传。只以朱子曰分注处是否。
今二典禹谟之传。皆朱子所定也。集传本先生所命。故蔡氏之自为传。往往引用先生说。而不以朱子曰别之。只连接成文。以见此传之皆出于先生指挥。而不由己意也。分注之朱子曰。是后儒之取语类中所论者补入之。
四岳四凶之党。而尧已知之。故举人辄吁。而至若巽位则曰汝能庸命。
四岳想亦贤者。非四凶之党也。鲧之才堪于治水。故四岳举之。非党恶也。
曰有鳏在下。鳏是童丱之通称否。
童丱是未冠者。岂通称以鳏也。既冠而无妻。始可谓鳏。
帝将降二女于虞。则必先告于舜家矣。舜虽不告于瞽叟。瞽叟必已知矣。知而虽逆命。命必乃达。岂阴谋于舜。而舜亦掩匿于父母也。若瞽叟前知而能阻事。则后来更何惮而不为。然则尧舜之事。不惟不正大。无乃疏阔乎。观四岳不格奸之语及益之往于田呼泣祗载见允若之语。则降帝女必在允若之后矣。舍此牛羊仓廪。而复何事乎往于田也。然则孟子之答人。只是随问而答之否。
所论良是。程子意固如此。
舜典篇题。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钦哉之下。以上之上字。无乃下字之误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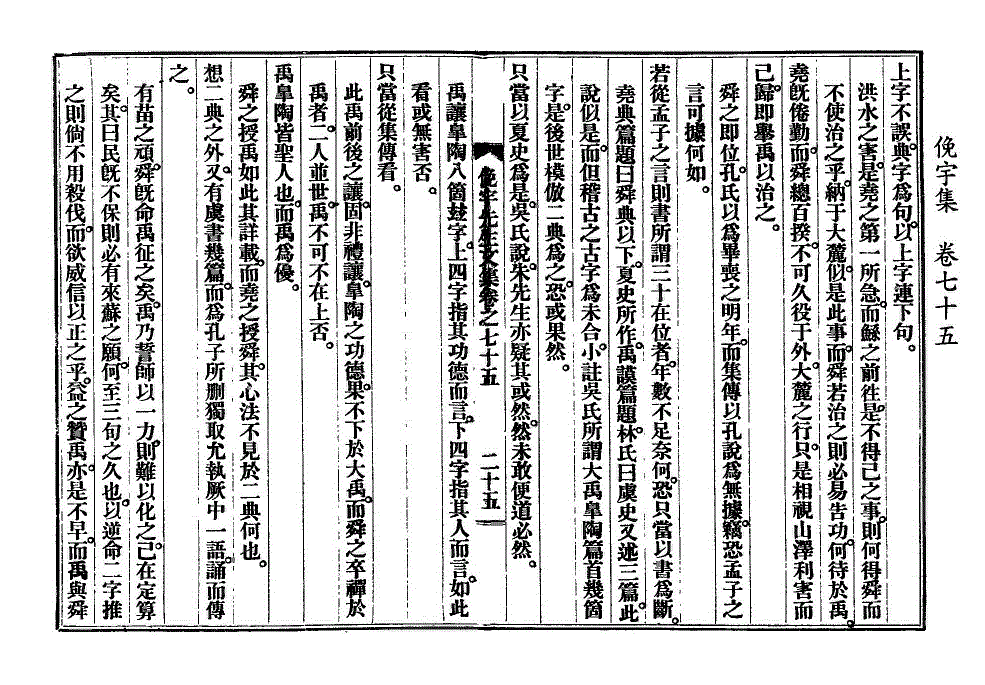 上字不误。典字为句。以上字连下句。
上字不误。典字为句。以上字连下句。洪水之害。是尧之第一所急。而鲧之前往。是不得已之事。则何得舜而不使治之乎。纳于大麓。似是此事。而舜若治之则必易告功。何待于禹。
尧既倦勤。而舜总百揆。不可久役于外。大麓之行。只是相视山泽利害而已。归即举禹以治之。
舜之即位。孔氏以为毕丧之明年。而集传以孔说为无据。窃恐孟子之言可据何如。
若从孟子之言则书所谓三十在位者。年数不足奈何。恐只当以书为断。
尧典篇题曰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禹谟篇题。林氏曰虞史又述三篇。此说似是。而但稽古之古字为未合。小注吴氏所谓大禹皋陶篇首几个字。是后世模仿二典为之。恐或果然。
只当以夏史为是。吴氏说。朱先生亦疑其或然。然未敢便道必然。
禹让皋陶八个玆字。上四字指其功德而言。下四字指其人而言。如此看或无害否。
只当从集传看。
此禹前后之让。固非礼让。皋陶之功德。果不下于大禹。而舜之卒禅于禹者。二人并世。禹不可不在上否。
禹皋陶皆圣人也。而禹为优。
舜之授禹如此其详载。而尧之授舜。其心法不见于二典何也。
想二典之外。又有虞书几篇。而为孔子所删独取允执厥中一语。诵而传之。
有苗之顽。舜既命禹征之矣。禹乃誓师以一力。则难以化之。已在定算矣。其曰民既不保则必有来苏之愿。何至三旬之久也。以逆命二字推之则倘不用杀伐。而欲威信以正之乎。益之赞禹。亦是不早。而禹与舜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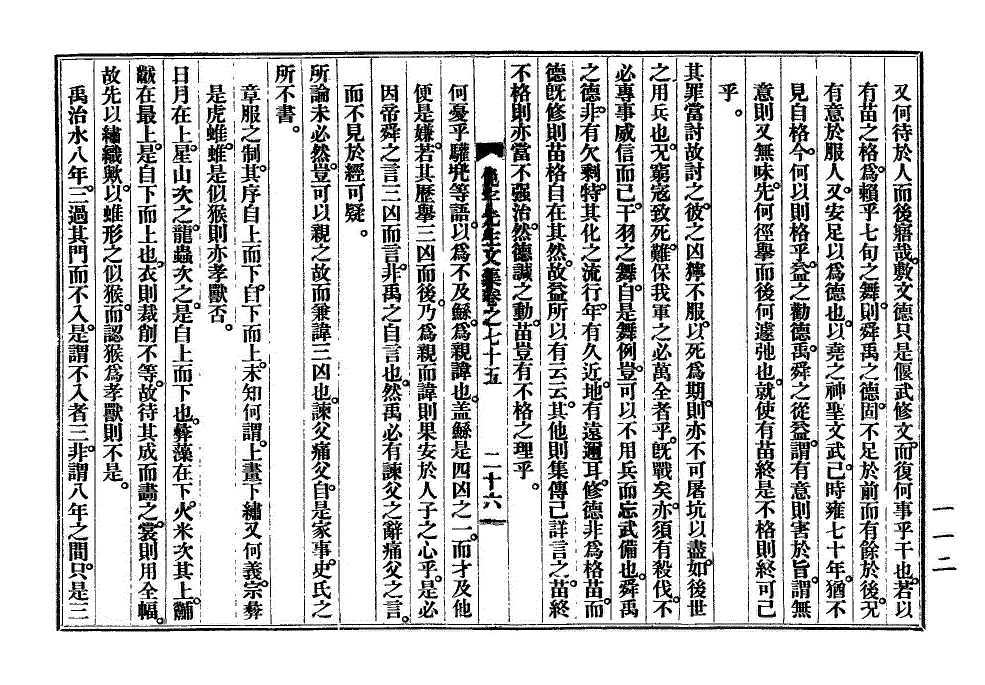 又何待于人而后寤哉。敷文德只是偃武修文。而复何事乎干也。若以有苗之格。为赖乎七旬之舞。则舜禹之德。固不足于前而有馀于后。况有意于服人。又安足以为德也。以尧之神圣文武。已时雍七十年。犹不见自格。今何以则格乎。益之劝德。禹舜之从益。谓有意则害于旨。谓无意则又无味。先何径举而后何遽弛也。就使有苗终是不格则终可已乎。
又何待于人而后寤哉。敷文德只是偃武修文。而复何事乎干也。若以有苗之格。为赖乎七旬之舞。则舜禹之德。固不足于前而有馀于后。况有意于服人。又安足以为德也。以尧之神圣文武。已时雍七十年。犹不见自格。今何以则格乎。益之劝德。禹舜之从益。谓有意则害于旨。谓无意则又无味。先何径举而后何遽弛也。就使有苗终是不格则终可已乎。其罪当讨故讨之。彼之凶狞不服。以死为期。则亦不可屠坑以尽。如后世之用兵也。况穷寇致死。难保我军之必万全者乎。既战矣。亦须有杀伐。不必专事威信而已。干羽之舞。自是舞例。岂可以不用兵而忘武备也。舜禹之德。非有欠剩。特其化之流行。年有久近。地有远迩耳。修德非为格苗。而德既修则苗格自在其然。故益所以有云云。其他则集传已详言之。苗终不格则亦当不强治。然德諴之动。苗岂有不格之理乎。
何忧乎驩兜等语。以为不及鲧。为亲讳也。盖鲧是四凶之一。而才及他便是嫌。若其历举三凶而后。乃为亲而讳则果安于人子之心乎。是必因帝舜之言三凶而言。非禹之自言也。然禹必有谏父之辞痛父之言。而不见于经可疑。
所论未必然。岂可以亲之故而兼讳三凶也。谏父痛父。自是家事。史氏之所不书。
章服之制。其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未知何谓。上画下绣又何义。宗彝是虎蜼蜼。是似猴则亦孝兽否。
日月在上。星山次之龙虫次之。是自上而下也。彝藻在下。火米次其上。黼黻在最上。是自下而上也。衣则裁削不等。故待其成而画之。裳则用全幅。故先以绣织欤。以蜼形之似猴。而认猴为孝兽则不是。
禹治水八年。三过其门而不入。是谓不入者三。非谓八年之间。只是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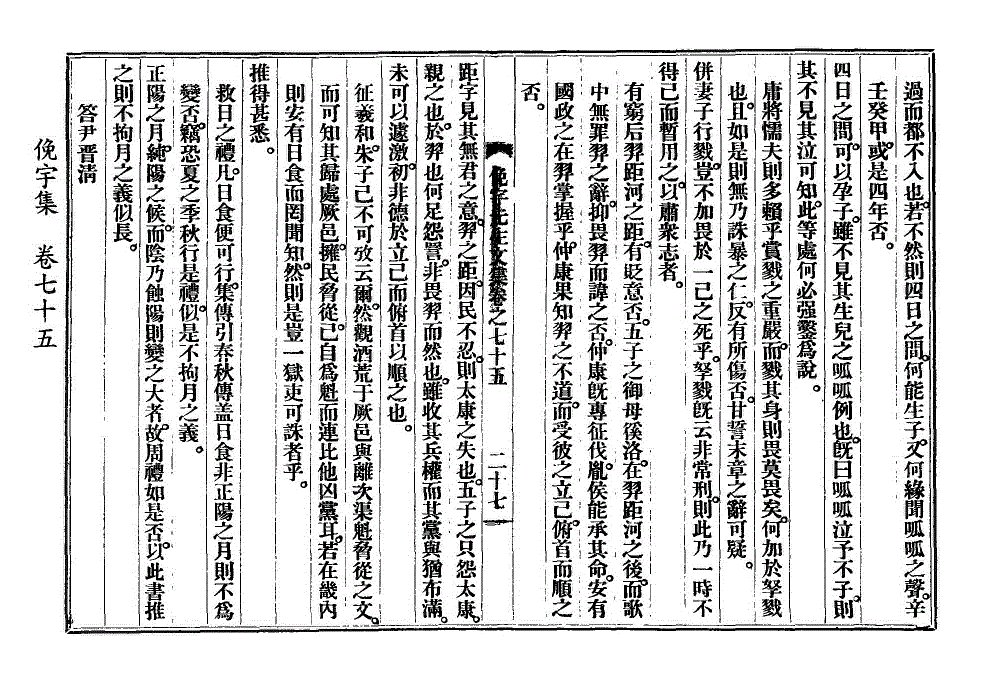 过而都不入也。若不然则四日之间。何能生子。又何缘闻呱呱之声。辛壬癸甲。或是四年否。
过而都不入也。若不然则四日之间。何能生子。又何缘闻呱呱之声。辛壬癸甲。或是四年否。四日之间。可以孕子。虽不见其生儿之呱呱例也。既曰呱呱泣予不子。则其不见其泣可知。此等处何必强凿为说。
庸将懦夫则多赖乎赏戮之重严。而戮其身则畏莫畏矣。何加于孥戮也。且如是则无乃诛暴之仁。反有所伤否。甘誓末章之辞可疑。
并妻子行戮。岂不加畏于一己之死乎。孥戮既云非常刑。则此乃一时不得已而暂用之。以肃众志者。
有穷后羿距河之距。有贬意否。五子之御母徯洛。在羿距河之后。而歌中无罪羿之辞。抑畏羿而讳之否。仲康既专征伐。胤侯能承其命。安有国政之在羿掌握乎。仲康果知羿之不道。而受彼之立己。俯首而顺之否。
距字见其无君之意。羿之距。因民不忍。则太康之失也。五子之只怨太康。亲之也。于羿也何足怨詈。非畏羿而然也。虽收其兵权而其党与犹布满。未可以遽激。初非德于立己而俯首以顺之也。
征羲和。朱子已不可考云尔。然观酒荒于厥邑与离次渠魁胁从之文。而可知其归处厥邑。拥民胁从。己自为魁而连比他凶党耳。若在畿内则安有日食而罔闻知。然则是岂一狱吏可诛者乎。
推得甚悉。
救日之礼。凡日食便可行。集传引春秋传盖日食非正阳之月则不为变否。窃恐夏之季秋行是礼。似是不拘月之义。
正阳之月。纯阳之候。而阴乃蚀阳则变之大者。故周礼如是否。以此书推之则不拘月之义似长。
答尹晋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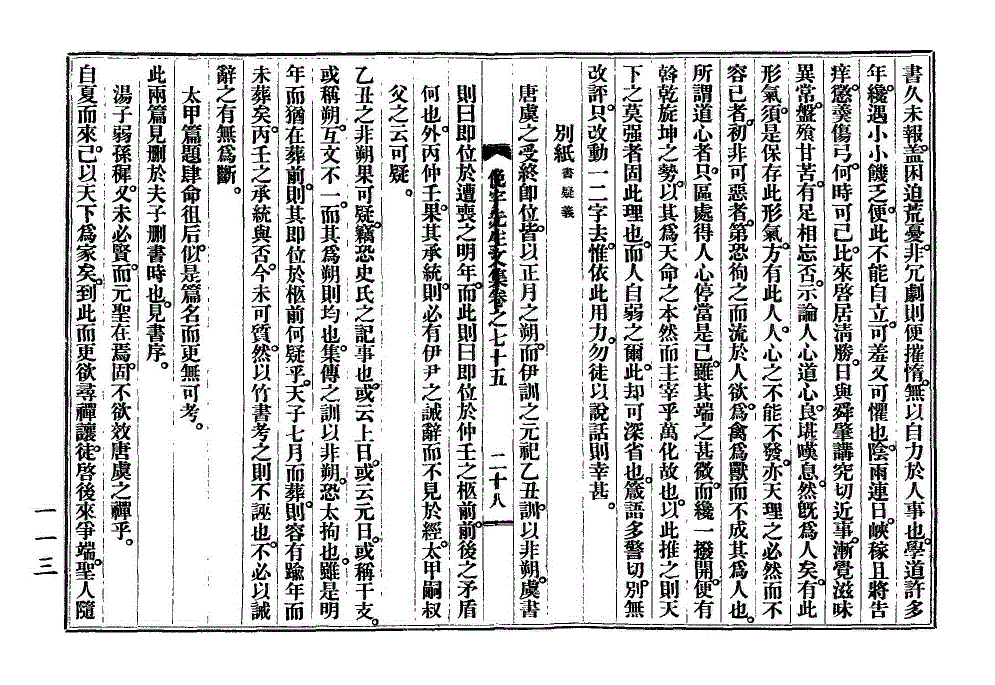 书久未报。盖困迫荒忧。非冗剧则便摧惰。无以自力于人事也。学道许多年。才遇小小饥乏。便此不能自立。可羞又可惧也。阴雨连日。峡稼且将告痒。惩羹伤弓。何时可已。比来启居清胜。日与舜肇讲究切近事。渐觉滋味异常。盘飧甘苦。有足相忘否。示论人心道心。良堪叹息。然既为人矣。有此形气。须是保存此形气。方有此人。人心之不能不发。亦天理之必然而不容己者。初非可恶者。第恐徇之而流于人欲。为禽为兽而不成其为人也。所谓道心者。只区处得人心停当是已。虽其端之甚微。而才一拨开。便有斡乾旋坤之势。以其为天命之本然而主宰乎万化故也。以此推之则天下之莫强者固此理也。而人自弱之尔。此却可深省也。箴语多警切。别无改评。只改动一二字去。惟依此用力。勿徒以说话则幸甚。
书久未报。盖困迫荒忧。非冗剧则便摧惰。无以自力于人事也。学道许多年。才遇小小饥乏。便此不能自立。可羞又可惧也。阴雨连日。峡稼且将告痒。惩羹伤弓。何时可已。比来启居清胜。日与舜肇讲究切近事。渐觉滋味异常。盘飧甘苦。有足相忘否。示论人心道心。良堪叹息。然既为人矣。有此形气。须是保存此形气。方有此人。人心之不能不发。亦天理之必然而不容己者。初非可恶者。第恐徇之而流于人欲。为禽为兽而不成其为人也。所谓道心者。只区处得人心停当是已。虽其端之甚微。而才一拨开。便有斡乾旋坤之势。以其为天命之本然而主宰乎万化故也。以此推之则天下之莫强者固此理也。而人自弱之尔。此却可深省也。箴语多警切。别无改评。只改动一二字去。惟依此用力。勿徒以说话则幸甚。别纸(书疑义)
唐虞之受终即位。皆以正月之朔。而伊训之元祀乙丑。训以非朔。虞书则曰即位于遭丧之明年。而此则曰即位于仲壬之柩前。前后之矛盾何也。外丙仲壬。果其承统。则必有伊尹之诫辞而不见于经。太甲嗣叔父之云可疑。
乙丑之非朔果可疑。窃恐史氏之记事也。或云上日。或云元日。或称干支。或称朔。互文不一。而其为朔则均也。集传之训以非朔。恐太拘也。虽是明年而犹在葬前。则其即位于柩前何疑乎。天子七月而葬。则容有踰年而未葬矣。丙壬之承统与否。今未可质。然以竹书考之则不诬也。不必以诫辞之有无为断。
太甲篇题肆命徂后。似是篇名而更无可考。
此两篇见删于夫子删书时也。见书序。
汤子弱孙稚。又未必贤。而元圣在焉。固不欲效唐虞之禅乎。
自夏而来。已以天下为家矣。到此而更欲寻禅让。徒启后来争端。圣人随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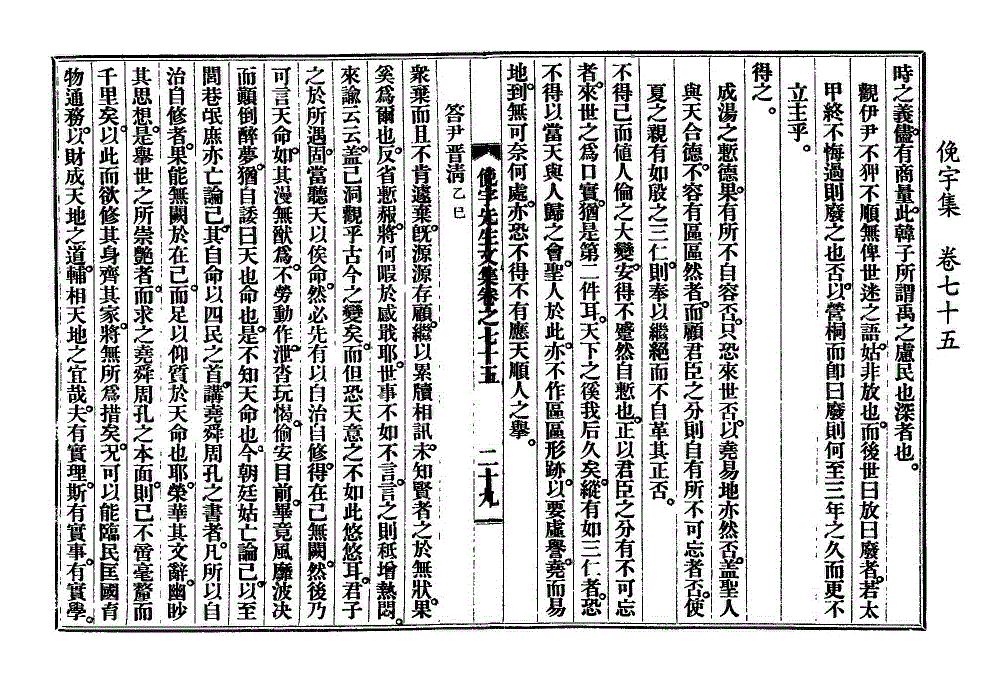 时之义。尽有商量。此韩子所谓禹之虑民也深者也。
时之义。尽有商量。此韩子所谓禹之虑民也深者也。观伊尹不狎不顺无俾世迷之语。姑非放也。而后世曰放曰废者。若太甲终不悔过则废之也否。以营桐而即曰废则何至三年之久而更不立主乎。
得之。
成汤之惭德。果有所不自容否。只恐来世否。以尧易地亦然否。盖圣人与天合德。不容有区区然者。而顾君臣之分则自有所不可忘者否。使夏之亲有如殷之三仁。则奉以继绝而不自革其正否。
不得已而值人伦之大变。安得不蹙然自惭也。正以君臣之分有不可忘者。来世之为口实。犹是第二件耳。天下之徯我后久矣。纵有如三仁者。恐不得以当天与人归之会。圣人于此。亦不作区区形迹。以要虚誉。尧而易地。到无可奈何处。亦恐不得不有应天顺人之举。
答尹晋清(乙巳)
众弃而且不肯遽弃。既源源存顾。继以累牍相讯。未知贤者之于无状。果奚为尔也。反省惭赧。将何暇于感戢耶。世事不如不言。言之则秪增热闷。来谕云云。盖已洞观乎古今之变矣。而但恐天意之不如此悠悠耳。君子之于所遇。固当听天以俟命。然必先有以自治自修。得在己无阙。然后乃可言天命。如其漫无猷为。不劳动作。泄沓玩愒。偷安目前。毕竟风靡波决而颠倒醉梦。犹自诿曰天也命也。是不知天命也。今朝廷姑亡论已。以至闾巷氓庶亦亡论已。其自命以四民之首。讲尧舜周孔之书者。凡所以自治自修者。果能无阙于在己。而足以仰质于天命也耶。荣华其文辞。幽眇其思想。是举世之所崇艳者。而求之尧舜周孔之本面。则已不啻毫釐而千里矣。以此而欲修其身齐其家。将无所为措矣。况可以能临民匡国育物通务。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哉。夫有实理。斯有实事。有实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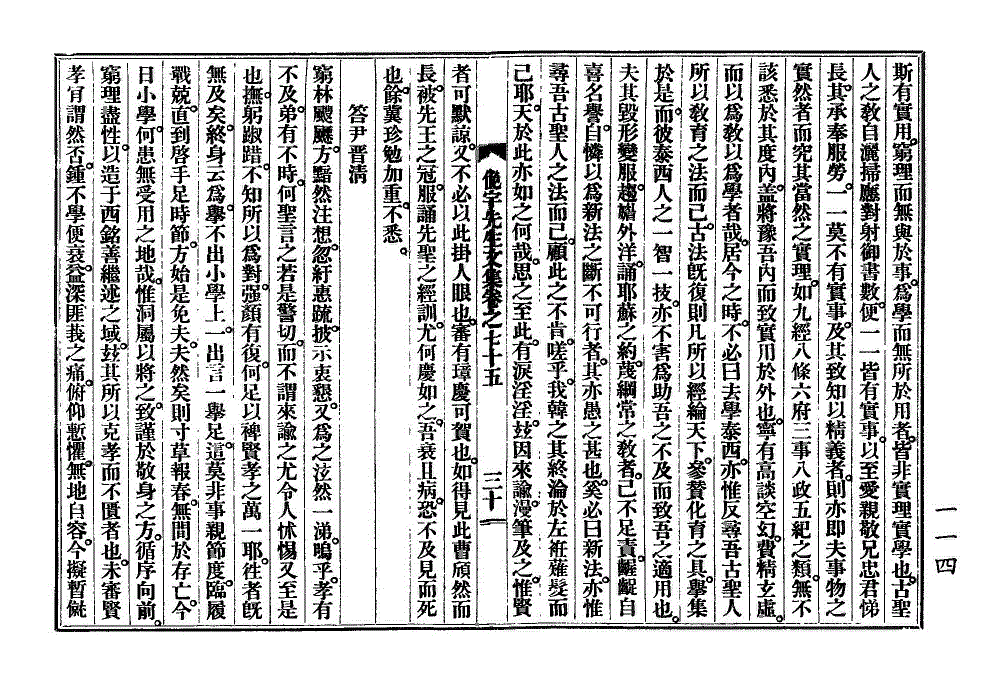 斯有实用。穷理而无与于事。为学而无所于用者。皆非实理实学也。古圣人之教自洒扫应对射御书数。便一一皆有实事。以至爱亲敬兄忠君悌长。其承奉服劳。一一莫不有实事。及其致知以精义者。则亦即夫事物之实然者而究其当然之实理。如九经八条六府三事八政五纪之类。无不该悉于其度内。盖将豫吾内而致实用于外也。宁有高谈空幻。费精玄虚。而以为教以为学者哉。居今之时。不必曰去学泰西。亦惟反寻吾古圣人所以教育之法而已。古法既复则凡所以经纶天下。参赞化育之具。举集于是。而彼泰西人之一智一技。亦不害为助吾之不及而致吾之适用也。夫其毁形变服。趋媚外洋。诵耶苏之约。蔑纲常之教者。已不足责。龌龊自喜名誉。自怜以为新法之断不可行者。其亦愚之甚也。奚必曰新法。亦惟寻吾古圣人之法而已。顾此之不肯。嗟乎。我韩之其终沦于左衽薙发而已耶。天于此亦如之何哉。思之至此。有泪淫淫。玆因来谕。漫笔及之。惟贤者可默谅。又不必以此挂人眼也。审有璋庆可贺也。如得见此曹颀然而长。被先王之冠。服诵先圣之经训。尤何庆如之。吾衰且病。恐不及见而死也。馀冀珍勉加重。不悉。
斯有实用。穷理而无与于事。为学而无所于用者。皆非实理实学也。古圣人之教自洒扫应对射御书数。便一一皆有实事。以至爱亲敬兄忠君悌长。其承奉服劳。一一莫不有实事。及其致知以精义者。则亦即夫事物之实然者而究其当然之实理。如九经八条六府三事八政五纪之类。无不该悉于其度内。盖将豫吾内而致实用于外也。宁有高谈空幻。费精玄虚。而以为教以为学者哉。居今之时。不必曰去学泰西。亦惟反寻吾古圣人所以教育之法而已。古法既复则凡所以经纶天下。参赞化育之具。举集于是。而彼泰西人之一智一技。亦不害为助吾之不及而致吾之适用也。夫其毁形变服。趋媚外洋。诵耶苏之约。蔑纲常之教者。已不足责。龌龊自喜名誉。自怜以为新法之断不可行者。其亦愚之甚也。奚必曰新法。亦惟寻吾古圣人之法而已。顾此之不肯。嗟乎。我韩之其终沦于左衽薙发而已耶。天于此亦如之何哉。思之至此。有泪淫淫。玆因来谕。漫笔及之。惟贤者可默谅。又不必以此挂人眼也。审有璋庆可贺也。如得见此曹颀然而长。被先王之冠。服诵先圣之经训。尤何庆如之。吾衰且病。恐不及见而死也。馀冀珍勉加重。不悉。答尹晋清
穷林飕飘。方黯然注想。忽纡惠疏。披示衷恳。又为之泫然一涕。呜乎。孝有不及。弟有不时。何圣言之若是警切。而不谓来谕之尤令人怵惕又至是也。抚躬踧踖。不知所以为对。强颜有复。何足以裨贤孝之万一耶。往者既无及矣。终身云为。举不出小学上。一出言一举足。这莫非事亲节度。临履战兢。直到启手足时节。方始是免夫。夫然矣则寸草报春。无间于存亡。今日小学。何患无受用之地哉。惟洞属以将之。致谨于敬身之方。循序向前。穷理尽性。以造于西铭善继述之域。玆其所以克孝而不匮者也。未审贤孝肯谓然否。钟不学便衰。益深匪莪之痛。俯仰惭惧。无地自容。今拟暂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五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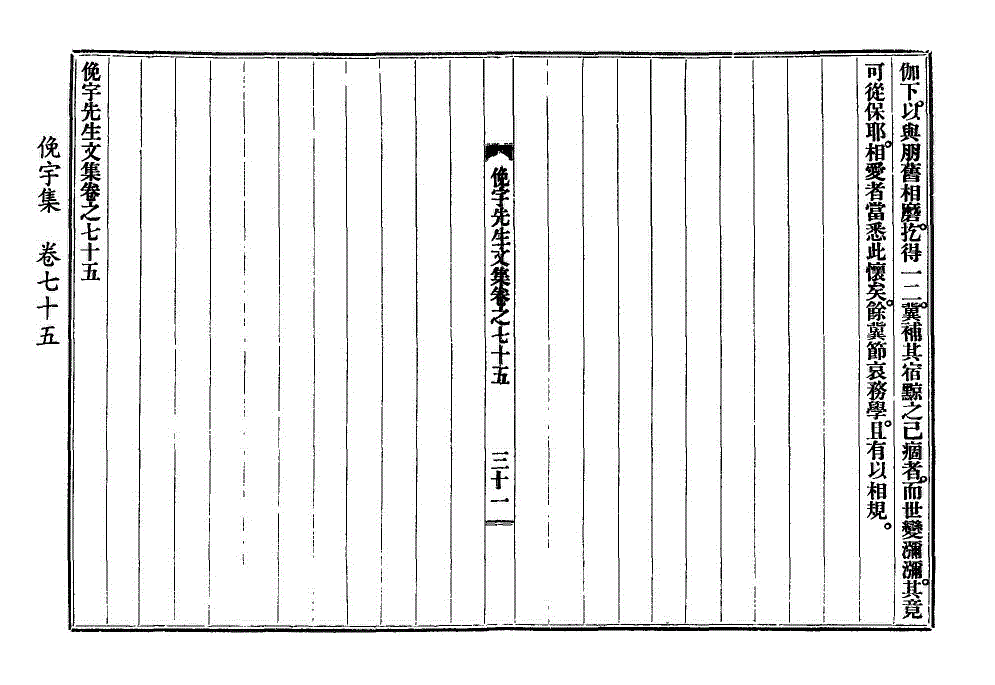 伽下。以与朋旧相磨。扢得一二。冀补其宿黥之已痼者。而世变瀰瀰。其竟可从保耶。相爱者当悉此怀矣。馀冀节哀务学。且有以相规。
伽下。以与朋旧相磨。扢得一二。冀补其宿黥之已痼者。而世变瀰瀰。其竟可从保耶。相爱者当悉此怀矣。馀冀节哀务学。且有以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