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x 页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书
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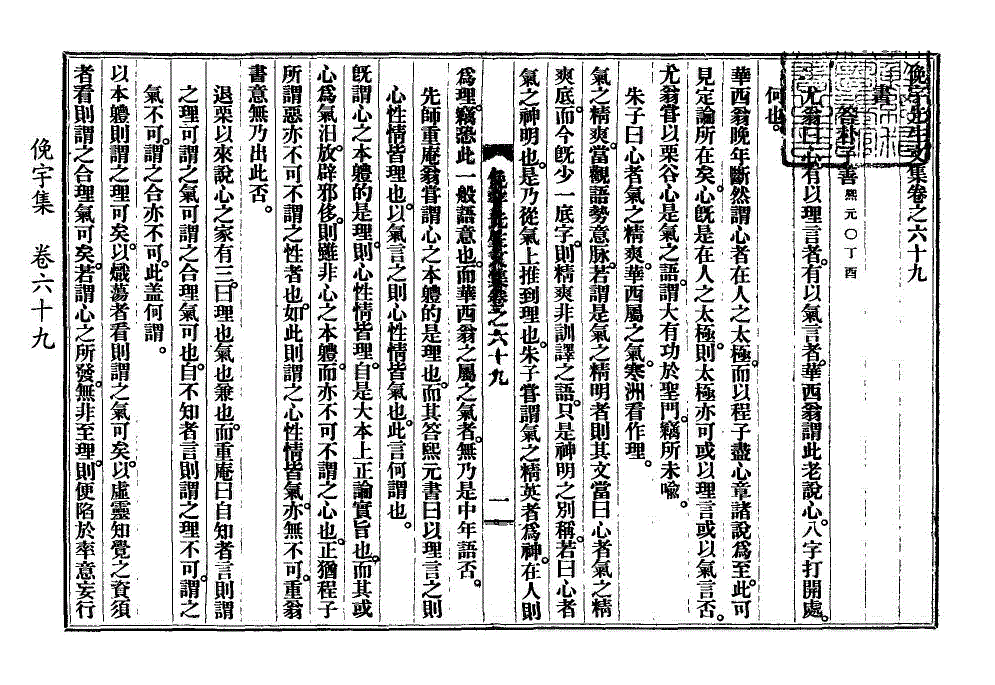 答朴子善(熙元○丁酉)
答朴子善(熙元○丁酉)尤翁曰心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华西翁谓此老说心。八字打开处。何也。
华西翁晚年断然谓心者在人之太极。而以程子尽心章诸说为至。此可见定论所在矣。心既是在人之太极。则太极亦可或以理言或以气言否。尤翁尝以栗谷心是气之语。谓大有功于圣门。窃所未喻。
朱子曰心者气之精爽。华西属之气。寒洲看作理。
气之精爽。当观语势意脉。若谓是气之精明者则其文当曰心者气之精爽底。而今既少一底字。则精爽非训译之语。只是神明之别称。若曰心者气之神明也。是乃从气上推到理也。朱子尝谓气之精英者为神。在人则为理。窃恐此一般语意也。而华西翁之属之气者。无乃是中年语否。
先师重庵翁尝谓心之本体的是理也。而其答熙元书曰以理言之则心性情皆理也。以气言之则心性情皆气也。此言何谓也。
既谓心之本体的是理。则心性情皆理。自是大本上正论实旨也。而其或心为气汩。放辟邪侈。则虽非心之本体。而亦不可不谓之心也。正犹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者也。如此则谓之心性情皆气。亦无不可。重翁书意无乃出此否。
退栗以来说心之家有三。曰理也气也兼也。而重庵曰自知者言则谓之理可谓之气可谓之合理气可也。自不知者言则谓之理不可。谓之气不可。谓之合亦不可。此盖何谓。
以本体则谓之理可矣。以炽荡者看则谓之气可矣。以虚灵知觉之资须者看则谓之合理气可矣。若谓心之所发。无非至理。则便陷于率意妄行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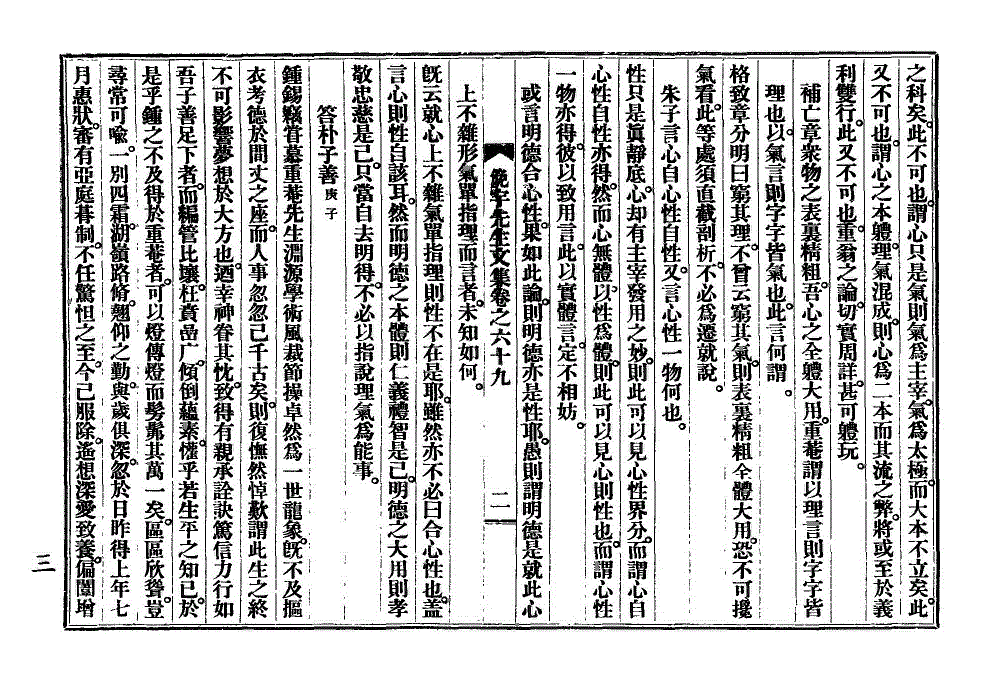 之科矣。此不可也。谓心只是气则气为主宰。气为太极。而大本不立矣。此又不可也。谓心之本体。理气混成。则心为二本而其流之弊。将或至于义利双行。此又不可也。重翁之论。切实周详。甚可体玩。
之科矣。此不可也。谓心只是气则气为主宰。气为太极。而大本不立矣。此又不可也。谓心之本体。理气混成。则心为二本而其流之弊。将或至于义利双行。此又不可也。重翁之论。切实周详。甚可体玩。补亡章众物之表里精粗。吾心之全体大用。重庵谓以理言则字字皆理也。以气言则字字皆气也。此言何谓。
格致章分明曰穷其理。不曾云穷其气。则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恐不可搀气看。此等处须直截剖析。不必为迁就说。
朱子言心自心性自性。又言心性一物何也。
性只是真静底。心却有主宰发用之妙。则此可以见心性界分。而谓心自心性自性亦得。然而心无体。以性为体。则此可以见心则性也。而谓心性一物亦得。彼以致用言。此以实体言。定不相妨。
或言明德合心性。果如此论。则明德亦是性耶。愚则谓明德是就此心上不杂形气单指理而言者。未知如何。
既云就心上不杂气单指理则性不在是耶。虽然亦不必曰合心性也。盖言心则性自该耳。然而明德之本体则仁义礼智是已。明德之大用则孝敬忠慈是已。只当自去明得。不必以指说理气为能事。
答朴子善(庚子)
钟锡窃尝慕重庵先生渊源学术风裁节操卓然为一世龙象。既不及抠衣考德于间丈之座。而人事忽忽已千古矣。则复怃然悼叹谓此生之终不可影响梦想于大方也。乃幸神眷其忱。致得有亲承诠诀笃信力行如吾子善足下者。而编管比壤。枉贲岩广。倾倒蕴素。欢乎若生平之知己。于是乎钟之不及得于重庵者。可以灯传灯而髣髴其万一矣。区区欣耸。岂寻常可喻。一别四霜。湖岭路脩。翘仰之勤。与岁俱深。忽于日昨得上年七月惠状。审有亚庭期制。不任惊怛之至。今已服除。遥想深爱致养。偏闱增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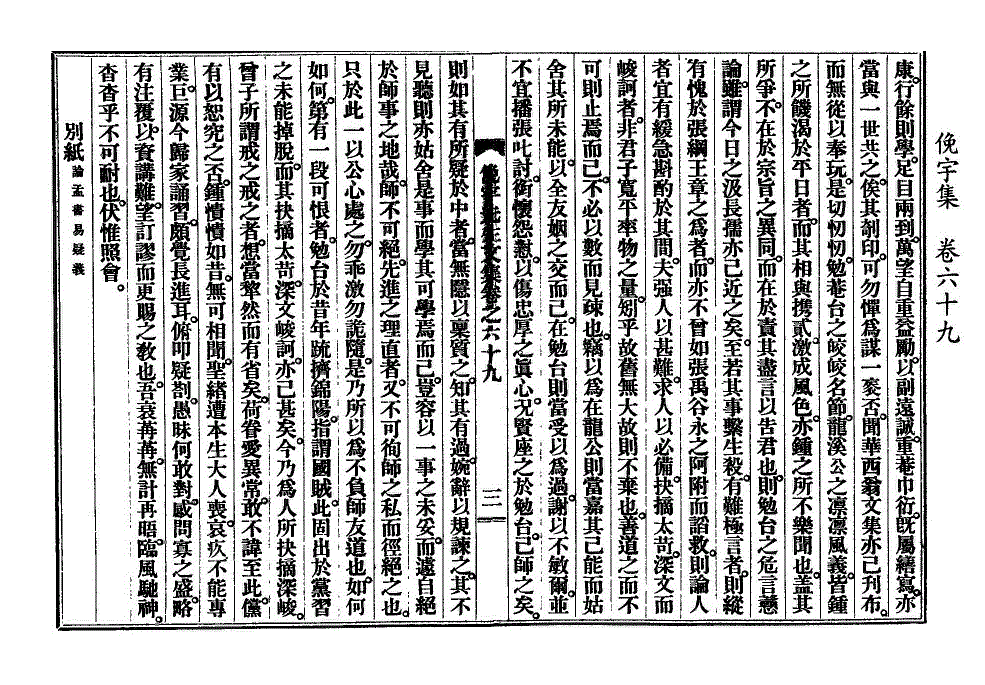 康。行馀则学。足目两到。万望自重益励。以副远诚。重庵巾衍。既属缮写。亦当与一世共之。俟其剞印。可勿惮为谋一帙否。闻华西翁文集亦已刊布。而无从以奉玩。是切忉忉。勉庵台之皎皎名节。龙溪公之凛凛风义。皆钟之所饥渴于平日者。而其相与携贰。激成风色。亦钟之所不乐闻也。盖其所争。不在于宗旨之异同。而在于责其尽言以告君也。则勉台之危言戆论。虽谓今日之汲长孺亦已近之矣。至若其事系生杀。有难极言者。则纵有愧于张纲王章之为者。而亦不曾如张禹谷永之阿附而谄救。则论人者宜有缓急斟酌于其间。夫强人以甚难。求人以必备。抉摘太苛。深文而峻诃者。非君子宽平率物之量。矧乎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善道之而不可则止焉而已。不必以数而见疏也。窃以为在龙公则当嘉其己能而姑舍其所未能。以全友姻之交而已。在勉台则当受以为过。谢以不敏尔。并不宜播张叱讨。衔怀怨怼。以伤忠厚之真心。况贤座之于勉台。已师之矣。则如其有所疑于中者。当无隐以禀质之。知其有过。婉辞以规谏之。其不见听则亦姑舍是事而学其可学焉而已。岂容以一事之未妥。而遽自绝于师事之地哉。师不可绝。先进之理直者。又不可徇师之私而径绝之也。只于此一以公心处之。勿乖激勿诡随。是乃所以为不负师友道也。如何如何。第有一段可恨者。勉台于昔年疏挤锦阳。指谓国贼。此固出于党习之未能掉脱。而其抉摘太苛。深文峻诃。亦已甚矣。今乃为人所抉摘深峻。曾子所谓戒之戒之者。想当犁然而有省矣。荷眷爱异常。敢不讳至此。傥有以恕究之否。钟愦愦如昔。无可相闻。圣绪遭本生大人丧。哀疚不能专业。巨源今归家诵习。颇觉长进耳。俯叩疑劄。愚昧何敢对。感问寡之盛。略有注覆。以资讲难。望订谬而更赐之教也。吾衰苒苒。无计再晤。临风驰神。杳杳乎不可耐也。伏惟照会。
康。行馀则学。足目两到。万望自重益励。以副远诚。重庵巾衍。既属缮写。亦当与一世共之。俟其剞印。可勿惮为谋一帙否。闻华西翁文集亦已刊布。而无从以奉玩。是切忉忉。勉庵台之皎皎名节。龙溪公之凛凛风义。皆钟之所饥渴于平日者。而其相与携贰。激成风色。亦钟之所不乐闻也。盖其所争。不在于宗旨之异同。而在于责其尽言以告君也。则勉台之危言戆论。虽谓今日之汲长孺亦已近之矣。至若其事系生杀。有难极言者。则纵有愧于张纲王章之为者。而亦不曾如张禹谷永之阿附而谄救。则论人者宜有缓急斟酌于其间。夫强人以甚难。求人以必备。抉摘太苛。深文而峻诃者。非君子宽平率物之量。矧乎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善道之而不可则止焉而已。不必以数而见疏也。窃以为在龙公则当嘉其己能而姑舍其所未能。以全友姻之交而已。在勉台则当受以为过。谢以不敏尔。并不宜播张叱讨。衔怀怨怼。以伤忠厚之真心。况贤座之于勉台。已师之矣。则如其有所疑于中者。当无隐以禀质之。知其有过。婉辞以规谏之。其不见听则亦姑舍是事而学其可学焉而已。岂容以一事之未妥。而遽自绝于师事之地哉。师不可绝。先进之理直者。又不可徇师之私而径绝之也。只于此一以公心处之。勿乖激勿诡随。是乃所以为不负师友道也。如何如何。第有一段可恨者。勉台于昔年疏挤锦阳。指谓国贼。此固出于党习之未能掉脱。而其抉摘太苛。深文峻诃。亦已甚矣。今乃为人所抉摘深峻。曾子所谓戒之戒之者。想当犁然而有省矣。荷眷爱异常。敢不讳至此。傥有以恕究之否。钟愦愦如昔。无可相闻。圣绪遭本生大人丧。哀疚不能专业。巨源今归家诵习。颇觉长进耳。俯叩疑劄。愚昧何敢对。感问寡之盛。略有注覆。以资讲难。望订谬而更赐之教也。吾衰苒苒。无计再晤。临风驰神。杳杳乎不可耐也。伏惟照会。别纸(论孟书易疑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4L 页
 论语序说牛人注刍柱之刍。柱恐牲之误。下刍字似是衍。
论语序说牛人注刍柱之刍。柱恐牲之误。下刍字似是衍。印本作牲字。下刍字亦不是衍。衍则不成文。盖谓经所云刍。是养牲之刍也。其上与字属牧人充人为句。乃助语之疑辞。
孔子之与阳货也。不啻龙豕之相悬也。其为貌像。何尝彷佛于彼此。而至见拘于匡耶。
孔子之圣。在德不在貌。货亦人也。其貌之与圣人略相彷佛。何至如龙豕之殊族也。自善观者观之则貌虽同而德容之畅于四肢者。宜不啻龙豕之别也。匡人凡民也。无怪乎其徒见他骨相之粗。而未及察于威仪辞气之符也。
书社。如今所谓户籍是否。饶氏谓书会者何义。
从索隐说则诚如今之户籍。从饶说则想元时封邑之特恩书下者谓之书会。然二说俱生硬不顺。今未敢知。抑楚之俗。别有田邑以养读书之士。而名之曰书社欤。不然则书社只是地名。如齐之尼溪之田欤。
以孟子序说例之则程子曰诸条。当用又曰之例。而此却连称程子曰者。盖以明道伊川语之不同欤。
此四条。并伊川语。以其各为一意。故分段立文。而每称程子曰。孟子序说程子六条。非必尽是伊川语。而以其统论孟子人品功德。只是一意。故连书圈别。而谓之又曰欤。
或问谢氏杨氏说之过与实。而朱子答以尹氏最实。不及杨氏。恐有诖误。
此语类大雅录。无诖误耳。盖不许杨氏之实也。朱先生尝问论语精义自二程外孰得。童蜚卿对曰龟山胜。先生曰龟山好引證。未说本意。且将别说折过人。若看他本说未分明。并连所引失之。此是一病。又问杨仲思。对曰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说为简当。先生曰却是和靖说得的当。今此大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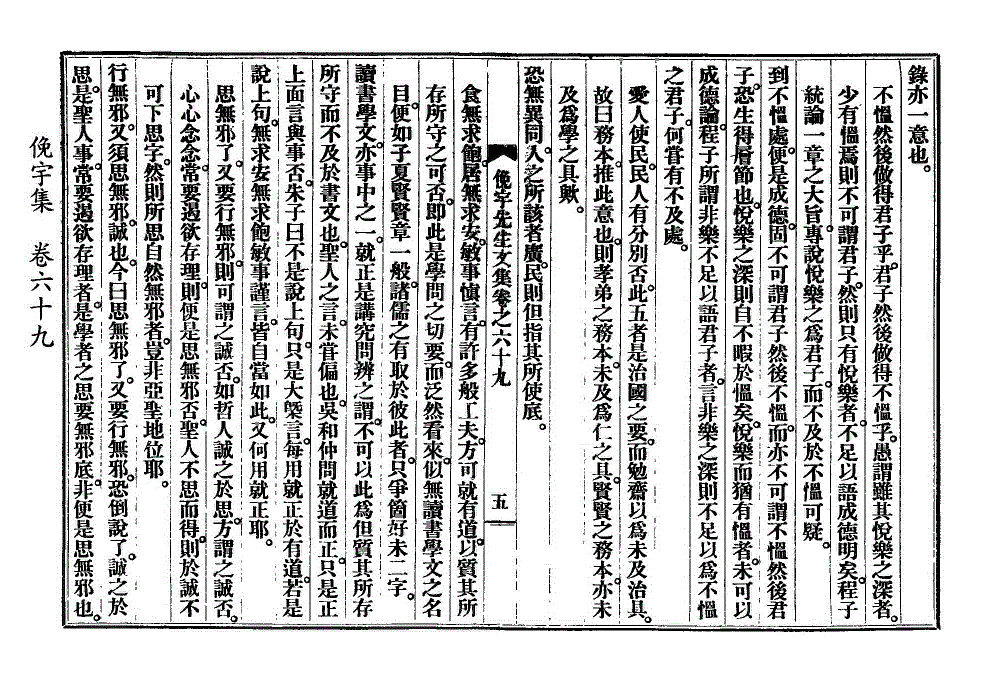 录亦一意也。
录亦一意也。不愠然后做得君子乎。君子然后做得不愠乎。愚谓虽其悦乐之深者。少有愠焉则不可谓君子。然则只有悦乐者。不足以语成德明矣。程子统论一章之大旨。专说悦乐之为君子。而不及于不愠可疑。
到不愠处。便是成德。固不可谓君子然后不愠。而亦不可谓不愠然后君子。恐生得层节也。悦乐之深则自不暇于愠矣。悦乐而犹有愠者。未可以成德论。程子所谓非乐不足以语君子者。言非乐之深则不足以为不愠之君子。何尝有不及处。
爱人使民。民人有分别否。此五者是治国之要。而勉斋以为未及治具。故曰务本。推此意也。则孝弟之务本。未及为仁之具。贤贤之务本。亦未及为学之具欤。
恐无异同。人之所该者广。民则但指其所使底。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事慎言。有许多般工夫。方可就有道。以质其所存所守之可否。即此是学问之切要。而泛然看来。似无读书学文之名目。便如子夏贤贤章一般。诸儒之有取于彼此者。只争个好未二字。
读书学文。亦事中之一。就正是讲究问辨之谓。不可以此为但质其所存所守而不及于书文也。圣人之言。未尝偏也。吴和仲问就道而正。只是正上面言与事否。朱子曰不是说上句。只是大槩言。每用就正于有道。若是说上句。无求安无求饱敏事谨言。皆自当如此。又何用就正耶。
思无邪了。又要行无邪。则可谓之诚否。如哲人诚之于思。方谓之诚否。心心念念。常要遏欲存理。则便是思无邪否。圣人不思而得。则于诚不可下思字。然则所思自然无邪者。岂非亚圣地位耶。
行无邪。又须思无邪。诚也。今曰思无邪了。又要行无邪。恐倒说了。诚之于思。是圣人事。常要遏欲存理者。是学者之思要无邪底。非便是思无邪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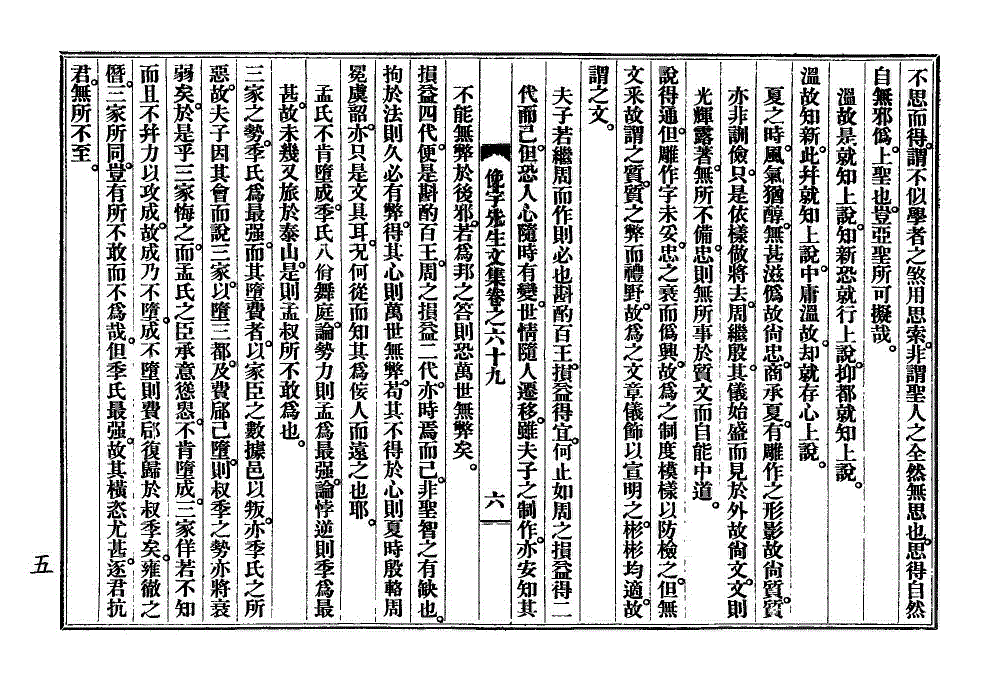 不思而得。谓不似学者之煞用思索。非谓圣人之全然无思也。思得自然自无邪伪。上圣也。岂亚圣所可拟哉。
不思而得。谓不似学者之煞用思索。非谓圣人之全然无思也。思得自然自无邪伪。上圣也。岂亚圣所可拟哉。温故是就知上说。知新恐就行上说。抑都就知上说。
温故知新。此并就知上说。中庸温故。却就存心上说。
夏之时。风气犹醇。无甚滋伪故尚忠。商承夏。有雕作之形影故尚质。质亦非训俭。只是依样做将去。周继殷。其仪始盛而见于外故尚文。文则光辉露著。无所不备。忠则无所事于质文而自能中道。
说得通。但雕作字未妥。忠之衰而伪兴。故为之制度模样以防检之。但无文采故谓之质。质之弊而礼野。故为之文章仪饰以宣明之。彬彬均适。故谓之文。
夫子若继周而作则必也斟酌百王。损益得宜。何止如周之损益得二代而已。但恐人心随时有变。世情随人迁移。虽夫子之制作。亦安知其不能无弊于后邪。若为邦之答则恐万世无弊矣。
损益四代。便是斟酌百王。周之损益二代。亦时焉而已。非圣智之有缺也。拘于法则久必有弊。得其心则万世无弊。苟其不得于心则夏时殷辂周冕虞韶。亦只是文具耳。况何从而知其为佞人而远之也耶。
孟氏不肯堕成。季氏八佾舞庭。论势力则孟为最强。论悖逆则季为最甚。故未几又旅于泰山。是则孟叔所不敢为也。
三家之势。季氏为最强。而其堕费者。以家臣之数据邑以叛。亦季氏之所恶。故夫子因其会而说三家。以堕三都。及费郈已堕。则叔季之势亦将衰弱矣。于是乎三家悔之。而孟氏之臣承意怂恿。不肯堕成。三家佯若不知而且不并力以攻成。故成乃不堕。成不堕则费郈复归于叔季矣。雍彻之僭。三家所同。岂有所不敢而不为哉。但季氏最强。故其横恣尤甚。逐君抗君。无所不至。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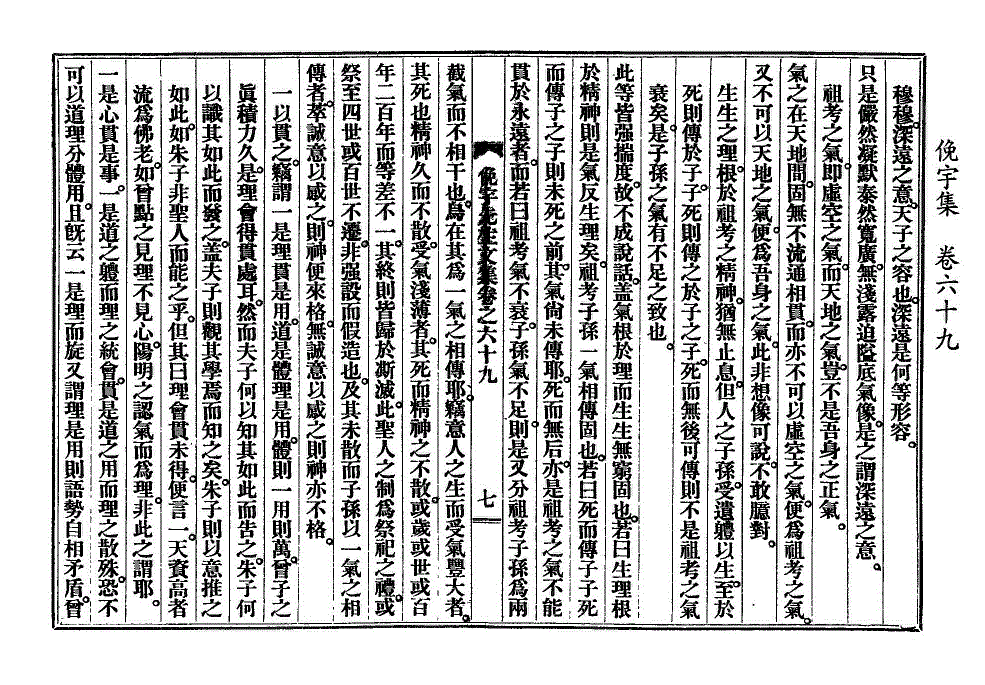 穆穆。深远之意。天子之容也。深远是何等形容。
穆穆。深远之意。天子之容也。深远是何等形容。只是俨然凝默泰然宽广。无浅露迫隘底气像。是之谓深远之意。
祖考之气。即虚空之气。而天地之气。岂不是吾身之正气。
气之在天地间。固无不流通相贯。而亦不可以虚空之气。便为祖考之气。又不可以天地之气。便为吾身之气。此非想像可说。不敢臆对。
生生之理。根于祖考之精神。犹无止息。但人之子孙。受遗体以生。至于死则传于子。子死则传之于子之子。死而无后可传则不是祖考之气衰矣。是子孙之气有不足之致也。
此等皆强揣度。故不成说话。盖气根于理而生生无穷固也。若曰生理根于精神则是气反生理矣。祖考子孙一气相传固也。若曰死而传子子死而传子之子则未死之前。其气尚未传耶。死而无后。亦是祖考之气不能贯于永远者。而若曰祖考气不衰。子孙气不足。则是又分祖考子孙为两截气而不相干也。乌在其为一气之相传耶。窃意人之生而受气丰大者。其死也精神久而不散。受气浅薄者。其死而精神之不散。或岁或世或百年二百年而等差不一。其终则皆归于凘灭。此圣人之制为祭祀之礼。或祭至四世或百世不迁。非强设而假造也。及其未散而子孙以一气之相传者。萃诚意以感之。则神便来格。无诚意以感之则神亦不格。
一以贯之。窃谓一是理贯是用。道是体理是用。体则一用则万。曾子之真积力久。是理会得贯处耳。然而夫子何以知其如此而告之。朱子何以识其如此而发之。盖夫子则观其学焉而知之矣。朱子则以意推之如此。如朱子非圣人而能之乎。但其曰理会贯未得。便言一。天资高者流为佛老。如曾点之见理不见心。阳明之认气而为理。非此之谓耶。
一是心贯是事。一是道之体而理之统会。贯是道之用而理之散殊。恐不可以道理分体用。且既云一是理而旋又谓理是用则语势自相矛盾。曾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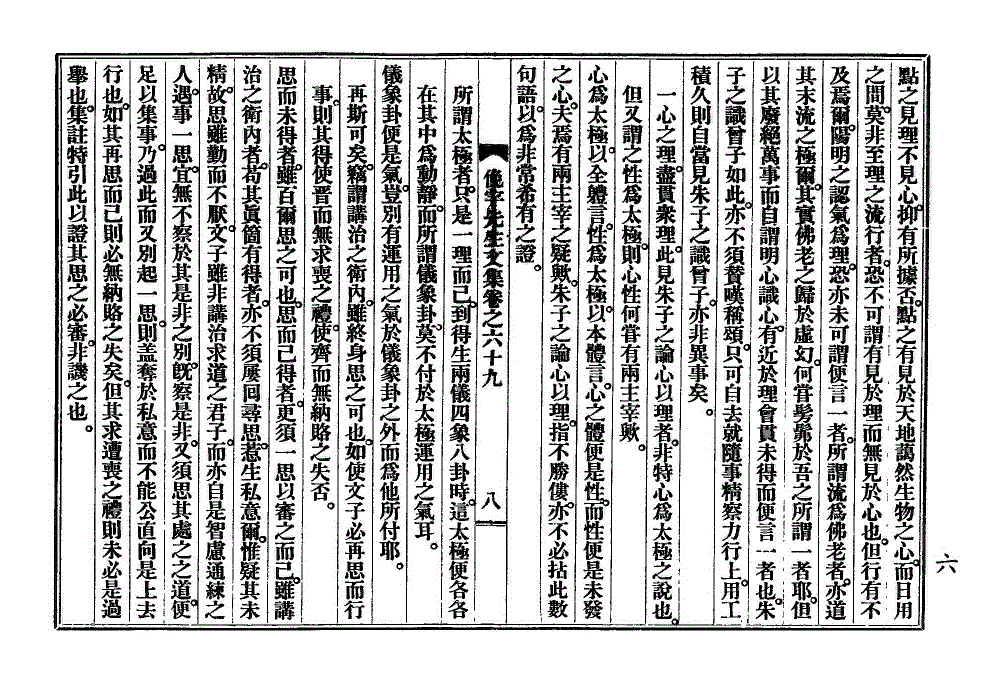 点之见理不见心。抑有所据否。点之有见于天地蔼然生物之心。而日用之间。莫非至理之流行者。恐不可谓有见于理而无见于心也。但行有不及焉尔。阳明之认气为理。恐亦未可谓便言一者。所谓流为佛老者。亦道其末流之极尔。其实佛老之归于虚幻。何尝髣髴于吾之所谓一者耶。但以其废绝万事而自谓明心识心。有近于理会贯未得而便言一者也。朱子之识曾子如此。亦不须赞叹称颂。只可自去就随事精察力行上。用工积久则自当见朱子之识曾子。亦非异事矣。
点之见理不见心。抑有所据否。点之有见于天地蔼然生物之心。而日用之间。莫非至理之流行者。恐不可谓有见于理而无见于心也。但行有不及焉尔。阳明之认气为理。恐亦未可谓便言一者。所谓流为佛老者。亦道其末流之极尔。其实佛老之归于虚幻。何尝髣髴于吾之所谓一者耶。但以其废绝万事而自谓明心识心。有近于理会贯未得而便言一者也。朱子之识曾子如此。亦不须赞叹称颂。只可自去就随事精察力行上。用工积久则自当见朱子之识曾子。亦非异事矣。一心之理。尽贯众理。此见朱子之论心以理者。非特心为太极之说也。但又谓之性为太极。则心性何尝有两主宰欤。
心为太极。以全体言。性为太极。以本体言。心之体便是性。而性便是未发之心。夫焉有两主宰之疑欤。朱子之论心以理。指不胜偻。亦不必拈此数句语。以为非常希有之證。
所谓太极者。只是一理而已。到得生两仪四象八卦时。这太极便各各在其中为动静。而所谓仪象卦。莫不付于太极运用之气耳。
仪象卦便是气。岂别有运用之气于仪象卦之外而为他所付耶。
再斯可矣。窃谓讲治之卫内。虽终身思之可也。如使文子必再思而行事。则其得使晋而无求丧之礼。使齐而无纳赂之失否。
思而未得者。虽百尔思之可也。思而已得者。更须一思以审之而已。虽讲治之卫内者。苟其真个有得者。亦不须屡回寻思。惹生私意尔。惟疑其未精。故思虽勤而不厌。文子虽非讲治求道之君子。而亦自是智虑通练之人。遇事一思。宜无不察于其是非之别。既察是非。又须思其处之之道。便足以集事。乃过此而又别起一思。则盖夺于私意而不能公直向是上去行也。如其再思而已则必无纳赂之失矣。但其求遭丧之礼则未必是过举也。集注特引此以證其思之必审。非讥之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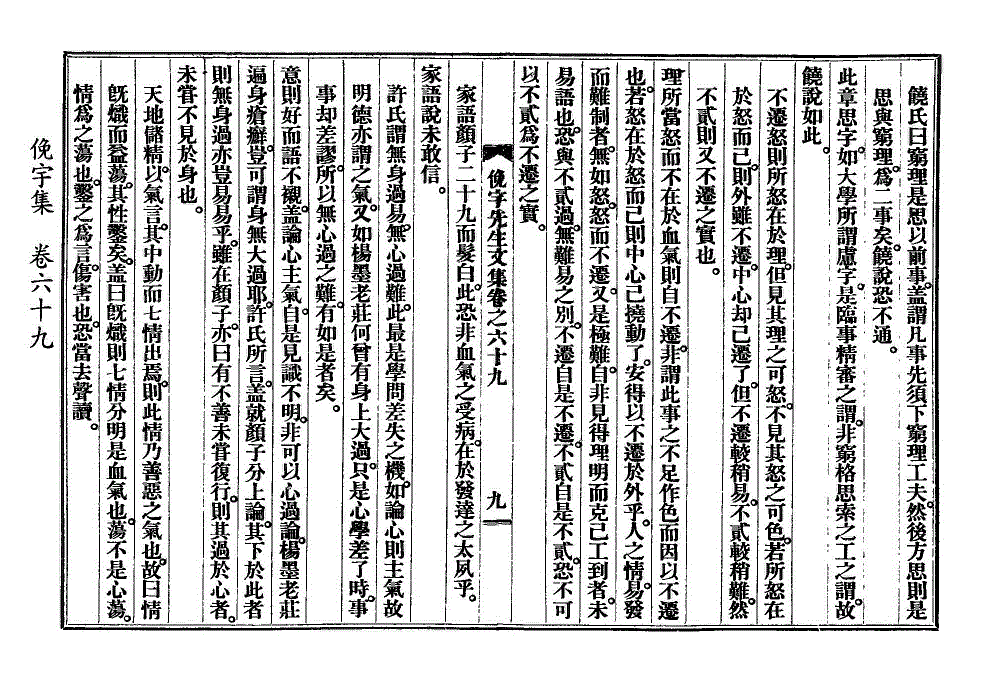 饶氏曰穷理是思以前事。盖谓凡事先须下穷理工夫。然后方思则是思与穷理。为二事矣。饶说恐不通。
饶氏曰穷理是思以前事。盖谓凡事先须下穷理工夫。然后方思则是思与穷理。为二事矣。饶说恐不通。此章思字。如大学所谓虑字。是临事精审之谓。非穷格思索之工之谓。故饶说如此。
不迁怒则所怒在于理。但见其理之可怒。不见其怒之可色。若所怒在于怒而已。则外虽不迁。中心却已迁了。但不迁较稍易。不贰较稍难。然不贰则又不迁之实也。
理所当怒而不在于血气则自不迁。非谓此事之不足作色而因以不迁也。若怒在于怒而已则中心已挠动了。安得以不迁于外乎。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无如怒。怒而不迁。又是极难。自非见得理明而克己工到者。未易语也。恐与不贰过。无难易之别。不迁自是不迁。不贰自是不贰。恐不可以不贰为不迁之实。
家语颜子二十九而发白。此恐非血气之受病。在于发达之太夙乎。
家语说未敢信。
许氏谓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此最是学问差失之机。如论心则主气故明德亦谓之气。又如杨墨老庄何曾有身上大过。只是心学差了时。事事却差谬。所以无心过之难。有如是者矣。
意则好而语不衬。盖论心主气。自是见识不明。非可以心过论。杨墨老庄遍身疮癣。岂可谓身无大过耶。许氏所言。盖就颜子分上论。其下于此者则无身过亦岂易易乎。虽在颜子。亦曰有不善未尝复行。则其过于心者。未尝不见于身也。
天地储精。以气言。其中动而七情出焉。则此情乃善恶之气也。故曰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盖曰既炽则七情分明是血气也。荡不是心荡。情为之荡也。凿之为言。伤害也。恐当去声读。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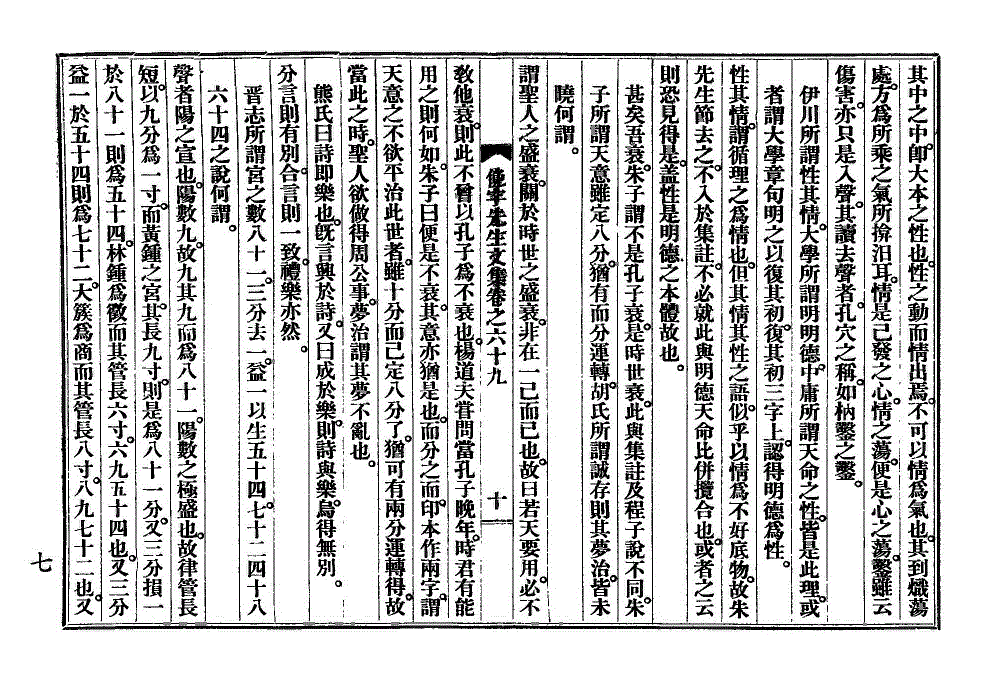 其中之中。即大本之性也。性之动而情出焉。不可以情为气也。其到炽荡处。方为所乘之气所掩汩耳。情是已发之心。情之荡。便是心之荡。凿虽云伤害。亦只是入声。其读去声者。孔穴之称。如枘凿之凿。
其中之中。即大本之性也。性之动而情出焉。不可以情为气也。其到炽荡处。方为所乘之气所掩汩耳。情是已发之心。情之荡。便是心之荡。凿虽云伤害。亦只是入声。其读去声者。孔穴之称。如枘凿之凿。伊川所谓性其情。大学所谓明明德。中庸所谓天命之性。皆是此理。或者谓大学章句明之以复其初。复其初三字上。认得明德为性。
性其情。谓循理之为情也。但其情其性之语。似乎以情为不好底物。故朱先生节去之。不入于集注。不必就此与明德天命比并揽合也。或者之云则恐见得是。盖性是明德之本体故也。
甚矣吾衰。朱子谓不是孔子衰。是时世衰。此与集注及程子说不同。朱子所谓天意虽定八分。犹有而分运转。胡氏所谓诚存则其梦治。皆未晓何谓。
谓圣人之盛衰。关于时世之盛衰。非在一己而已也。故曰若天要用。必不教他衰。则此不曾以孔子为不衰也。杨道夫尝问当孔子晚年时君有能用之则何如。朱子曰便是不衰。其意亦犹是也。而分之而。印本作两字。谓天意之不欲平治此世者。虽十分而已定八分了。犹可有两分运转得。故当此之时。圣人欲做得周公事。梦治谓其梦不乱也。
熊氏曰诗即乐也。既言兴于诗。又曰成于乐。则诗与乐。乌得无别。
分言则有别。合言则一致。礼乐亦然。
晋志所谓宫之数八十一。三分去一。益一以生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之说何谓。
声者阳之宣也。阳数九。故九其九而为八十一。阳数之极盛也。故律管长短。以九分为一寸。而黄钟之宫。其长九寸。则是为八十一分。又三分损一于八十一则为五十四。林钟为徵而其管长六寸。六九五十四也。又三分益一于五十四则为七十二。大簇为商而其管长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又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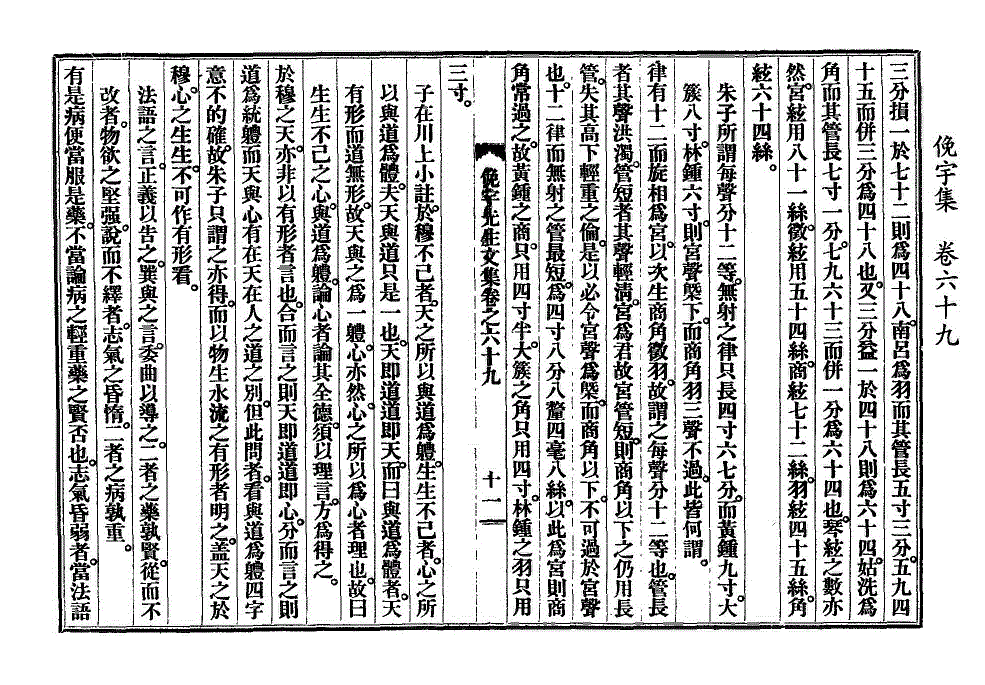 三分损一于七十二则为四十八。南吕为羽而其管长五寸三分。五九四十五而并三分为四十八也。又三分益一于四十八则为六十四。姑洗为角而其管长七寸一分。七九六十三而并一分为六十四也。琴弦之数亦然。宫弦用八十一丝。徵弦用五十四丝。商弦七十二丝。羽弦四十五丝。角弦六十四丝。
三分损一于七十二则为四十八。南吕为羽而其管长五寸三分。五九四十五而并三分为四十八也。又三分益一于四十八则为六十四。姑洗为角而其管长七寸一分。七九六十三而并一分为六十四也。琴弦之数亦然。宫弦用八十一丝。徵弦用五十四丝。商弦七十二丝。羽弦四十五丝。角弦六十四丝。朱子所谓每声分十二等。无射之律只长四寸六七分。而黄钟九寸。大簇八寸。林钟六寸。则宫声槩下。而商角羽三声不过。此皆何谓。
律有十二而旋相为宫。以次生商角徵羽。故谓之每声分十二等也。管长者其声洪浊。管短者其声轻清。宫为君故宫管短。则商角以下之仍用长管。失其高下轻重之伦。是以必令宫声为槩。而商角以下。不可过于宫声也。十二律而无射之管最短。为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丝。以此为宫则商角常过之。故黄钟之商。只用四寸半。大簇之角只用四寸。林钟之羽只用三寸。
子在川上小注。于穆不已者。天之所以与道为体。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与道为体。夫天与道只是一也。天即道道即天。而曰与道为体者。天有形而道无形。故天与之为一体。心亦然。心之所以为心者理也。故曰生生不已之心。与道为体。论心者论其全德。须以理言。方为得之。
于穆之天。亦非以有形者言也。合而言之则天即道道即心。分而言之则道为统体而天与心有在天在人之道之别。但此问者。看与道为体四字意不的确。故朱子只谓之亦得。而以物生水流之有形者明之。盖天之于穆。心之生生。不可作有形看。
法语之言。正义以告之。巽与之言。委曲以导之。二者之药孰贤。从而不改者。物欲之坚强。说而不绎者。志气之昏惰。二者之病孰重。
有是病便当服是药。不当论病之轻重药之贤否也。志气昏弱者。当法语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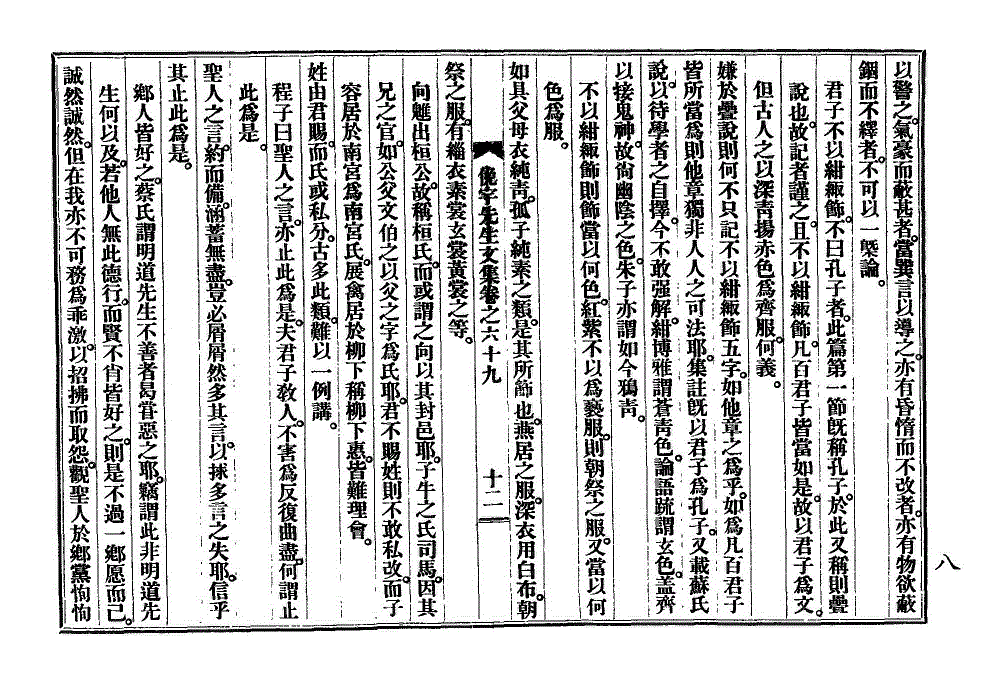 以警之。气豪而蔽甚者。当巽言以导之。亦有昏惰而不改者。亦有物欲蔽锢而不绎者。不可以一槩论。
以警之。气豪而蔽甚者。当巽言以导之。亦有昏惰而不改者。亦有物欲蔽锢而不绎者。不可以一槩论。君子不以绀緅饰。不曰孔子者。此篇第一节既称孔子。于此又称则叠说也。故记者谨之。且不以绀緅饰。凡百君子皆当如是。故以君子为文。但古人之以深青扬赤色为齐服。何义。
嫌于叠说则何不只记不以绀緅饰五字。如他章之为乎。如为凡百君子皆所当为则他章独非人人之可法耶。集注既以君子为孔子。又载苏氏说。以待学者之自择。今不敢强解。绀博雅谓苍青色。论语疏谓玄色。盖齐以接鬼神。故尚幽阴之色。朱子亦谓如今鸦青。
不以绀緅饰则饰当以何色。红紫不以为亵服。则朝祭之服。又当以何色为服。
如具父母衣纯青。孤子纯素之类。是其所饰也。燕居之服。深衣用白布。朝祭之服。有缁衣素裳玄裳黄裳之等。
向魋出桓公。故称桓氏。而或谓之向以其封邑耶。子牛之氏司马。因其兄之官。如公父文伯之以父之字为氏耶。君不赐姓则不敢私改。而子容居于南宫为南宫氏。展禽居于柳下称柳下惠。皆难理会。
姓由君赐。而氏或私分。古多此类。难以一例讲。
程子曰圣人之言。亦止此为是。夫君子教人。不害为反复曲尽。何谓止此为是。
圣人之言。约而备。涵蓄无尽。岂必屑屑然多其言。以救多言之失耶。信乎其止此为是。
乡人皆好之。蔡氏谓明道先生不善者曷尝恶之耶。窃谓此非明道先生何以及。若他人无此德行。而贤不肖皆好之。则是不过一乡愿而已。
诚然诚然。但在我亦不可务为乖激。以招拂而取怨。观圣人于乡党恂恂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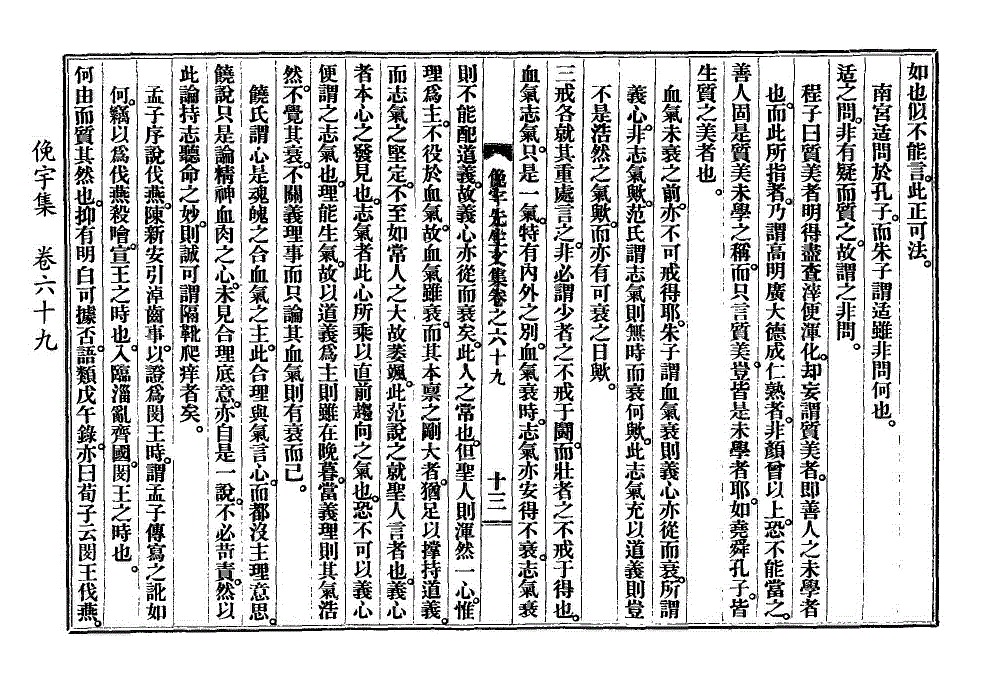 如也似不能言。此正可法。
如也似不能言。此正可法。南宫适问于孔子。而朱子谓适虽非问何也。
适之问。非有疑而质之。故谓之非问。
程子曰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妄谓质美者。即善人之未学者也。而此所指者。乃谓高明广大德成仁熟者。非颜曾以上。恐不能当之。
善人固是质美未学之称。而只言质美。岂皆是未学者耶。如尧舜孔子。皆生质之美者也。
血气未衰之前。亦不可戒得耶。朱子谓血气衰则义心亦从而衰。所谓义心。非志气欤。范氏谓志气则无时而衰何欤。此志气充以道义则岂不是浩然之气欤。而亦有可衰之日欤。
三戒各就其重处言之。非必谓少者之不戒于斗。而壮者之不戒于得也。血气志气。只是一气。特有内外之别。血气衰时。志气亦安得不衰。志气衰则不能配道义。故义心亦从而衰矣。此人之常也。但圣人则浑然一心。惟理为主。不役于血气。故血气虽衰。而其本禀之刚大者。犹足以撑持道义。而志气之坚定。不至如常人之大故萎飒。此范说之就圣人言者也。义心者本心之发见也。志气者此心所乘以直前趋向之气也。恐不可以义心便谓之志气也。理能生气。故以道义为主则虽在晚暮。当义理则其气浩然。不觉其衰。不关义理事而只论其血气则有衰而已。
饶氏谓心是魂魄之合血气之主。此合理与气言心。而都没主理意思。
饶说只是论精神血肉之心。未见合理底意。亦自是一说。不必苛责。然以此论持志听命之妙。则诚可谓隔靴爬痒者矣。
孟子序说伐燕。陈新安引淖齿事。以證为闵王时。谓孟子传写之讹如何。窃以为伐燕杀哙。宣王之时也。入临淄乱齐国。闵王之时也。
何由而质其然也。抑有明白可据否。语类戊午录。亦曰荀子云闵王伐燕。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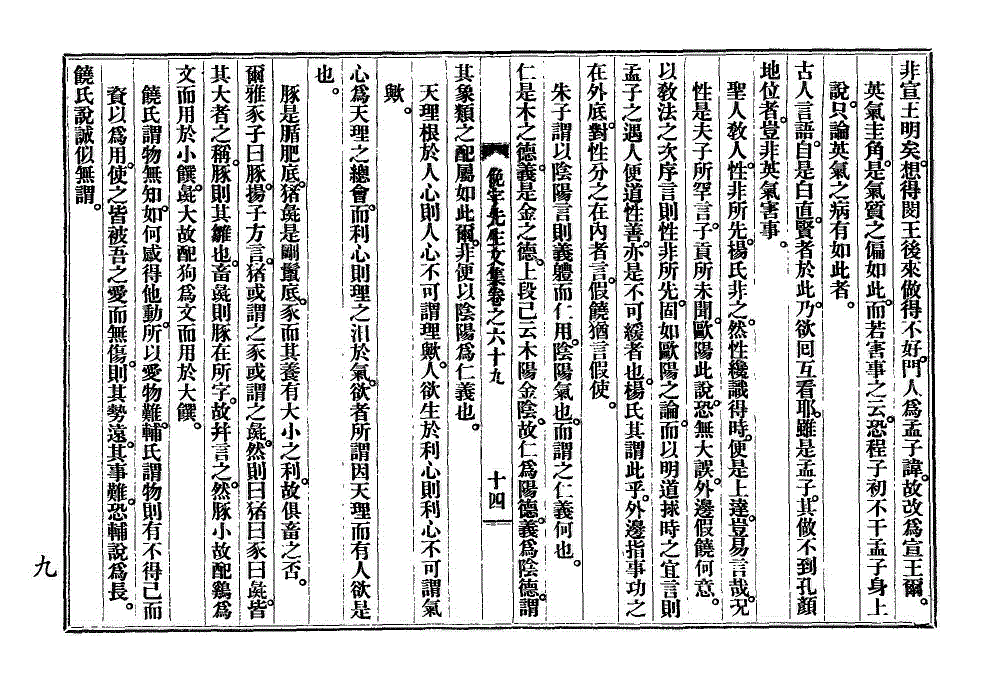 非宣王明矣。想得闵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
非宣王明矣。想得闵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英气圭角。是气质之偏如此。而若害事之云。恐程子初不干孟子身上说。只论英气之病有如此者。
古人言语。自是白直。贤者于此。乃欲回互看耶。虽是孟子。其做不到孔颜地位者。岂非英气害事。
圣人教人。性非所先。杨氏非之。然性才识得时。便是上达。岂易言哉。况性是夫子所罕言。子贡所未闻。欧阳此说。恐无大误。外边假饶何意。
以教法之次序言则性非所先。固如欧阳之论。而以明道救时之宜言则孟子之遇人便道性善。亦是不可缓者也。杨氏其谓此乎。外边指事功之在外底。对性分之在内者言。假饶犹言假使。
朱子谓以阴阳言则义体而仁用。阴阳气也。而谓之仁义何也。
仁是木之德。义是金之德。上段已云木阳金阴。故仁为阳德。义为阴德。谓其象类之配属如此尔。非便以阴阳为仁义也。
天理根于人心则人心不可谓理欤。人欲生于利心则利心不可谓气欤。
心为天理之总会。而利心则理之汩于气。欲者所谓因天理而有人欲是也。
豚是腯肥底。猪彘是刚鬣底。豕而其养有大小之利。故俱畜之否。
尔雅豕子曰豚。扬子方言。猪或谓之豕或谓之彘。然则曰猪曰豕曰彘。皆其大者之称。豚则其雏也。畜彘则豚在所字。故并言之。然豚小故配鸡为文而用于小馔。彘大故配狗为文而用于大馔。
饶氏谓物无知。如何感得他动。所以爱物难。辅氏谓物则有不得已而资以为用。使之皆被吾之爱而无伤。则其势远。其事难。恐辅说为长。
饶氏说诚似无谓。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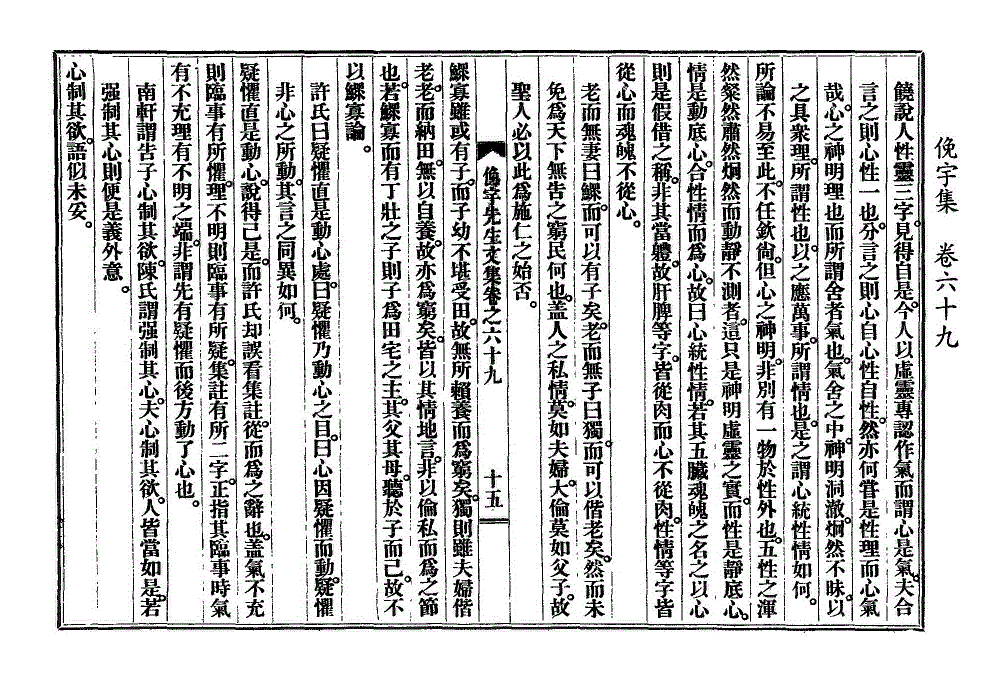 饶说人性灵三字。见得自是。今人以虚灵专认作气而谓心是气。夫合言之则心性一也。分言之则心自心性自性。然亦何尝是性理而心气哉。心之神明理也而所谓舍者气也。气舍之中。神明洞澈。炯然不昧。以之具众理。所谓性也。以之应万事。所谓情也。是之谓心统性情如何。
饶说人性灵三字。见得自是。今人以虚灵专认作气而谓心是气。夫合言之则心性一也。分言之则心自心性自性。然亦何尝是性理而心气哉。心之神明理也而所谓舍者气也。气舍之中。神明洞澈。炯然不昧。以之具众理。所谓性也。以之应万事。所谓情也。是之谓心统性情如何。所论不易至此。不任钦尚。但心之神明。非别有一物于性外也。五性之浑然粲然肃然炯然而动静不测者。这只是神明虚灵之实。而性是静底心。情是动底心。合性情而为心。故曰心统性情。若其五脏魂魄之名之以心则是假借之称。非其当体。故肝脾等字。皆从肉而心不从肉。性情等字皆从心而魂魄不从心。
老而无妻曰鳏。而可以有子矣。老而无子曰独。而可以偕老矣。然而未免为天下无告之穷民何也。盖人之私情。莫如夫妇。大伦莫如父子。故圣人必以此为施仁之始否。
鳏寡虽或有子。而子幼不堪受田。故无所赖养而为穷矣。独则虽夫妇偕老。老而纳田。无以自养。故亦为穷矣。皆以其情地言。非以伦私而为之节也。若鳏寡而有丁壮之子则子为田宅之主。其父其母。听于子而已。故不以鳏寡论。
许氏曰疑惧直是动心处。曰疑惧乃动心之目。曰心因疑惧而动。疑惧非心之所动。其言之同异如何。
疑惧直是动心。说得已是。而许氏却误看集注。从而为之辞也。盖气不充则临事有所惧。理不明则临事有所疑。集注有所二字。正指其临事时气有不充理有不明之端。非谓先有疑惧而后方动了心也。
南轩谓告子心制其欲。陈氏谓强制其心。夫心制其欲。人皆当如是。若强制其心则便是义外意。
心制其欲。语似未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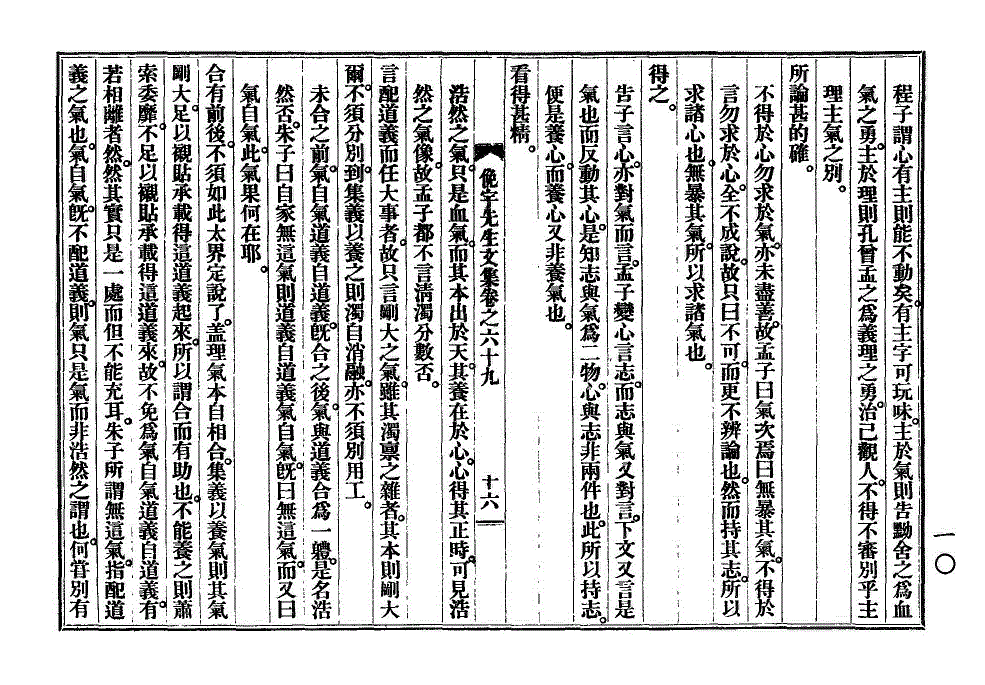 程子谓心有主则能不动矣。有主字可玩味。主于气则告黝舍之为血气之勇。主于理则孔曾孟之为义理之勇。治己观人。不得不审别乎主理主气之别。
程子谓心有主则能不动矣。有主字可玩味。主于气则告黝舍之为血气之勇。主于理则孔曾孟之为义理之勇。治己观人。不得不审别乎主理主气之别。所论甚的确。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亦未尽善。故孟子曰气次焉曰无暴其气。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全不成说。故只曰不可。而更不辨论也。然而持其志。所以求诸心也。无暴其气。所以求诸气也。
得之。
告子言心。亦对气而言。孟子变心言志。而志与气又对言。下文又言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是知志与气为二物。心与志非两件也。此所以持志。便是养心。而养心又非养气也。
看得甚精。
浩然之气。只是血气。而其本出于天。其养在于心。心得其正时。可见浩然之气像。故孟子都不言清浊分数否。
言配道义而任大事者。故只言刚大之气。虽其浊禀之杂者。其本则刚大尔。不须分别。到集义以养之则浊自消融。亦不须别用工。
未合之前。气自气道义自道义。既合之后。气与道义合为一体。是名浩然否。朱子曰自家无这气则道义自道义气自气。既曰无这气。而又曰气自气。此气果何在耶。
合有前后。不须如此太界定说了。盖理气本自相合。集义以养气则其气刚大。足以衬贴承载得这道义起来。所以谓合而有助也。不能养之则萧索委靡。不足以衬贴承载得这道义来。故不免为气自气道义自道义。有若相离者然。然其实只是一处而但不能充耳。朱子所谓无这气。指配道义之气也。气自气。既不配道义。则气只是气而非浩然之谓也。何尝别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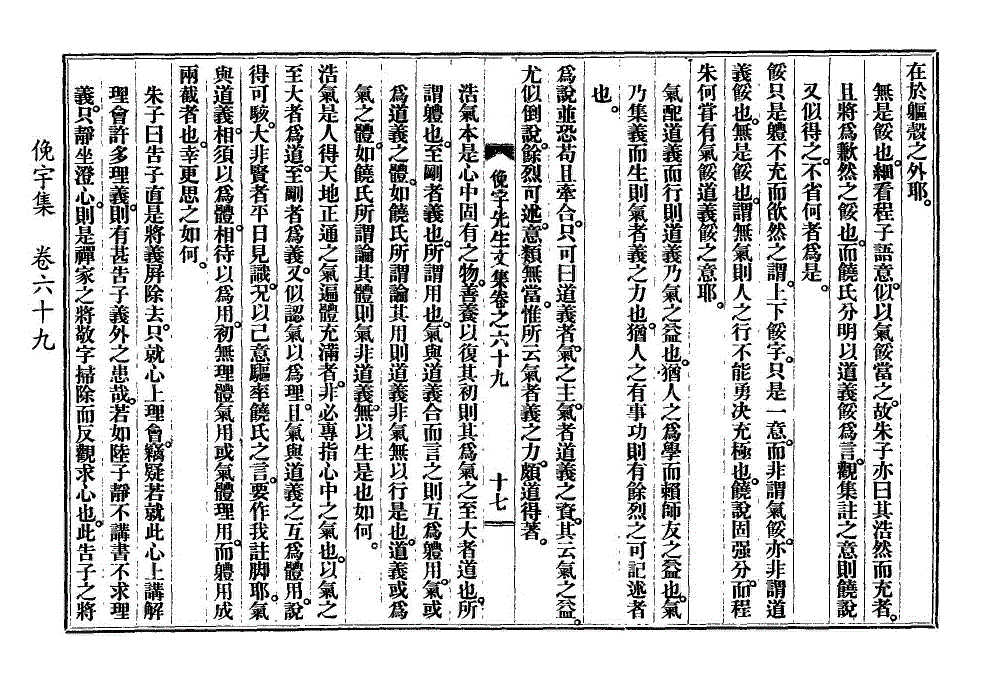 在于躯壳之外耶。
在于躯壳之外耶。无是馁也。细看程子语意。似以气馁当之。故朱子亦曰其浩然而充者。且将为歉然之馁也。而饶氏分明以道义馁为言。观集注之意则饶说又似得之。不省何者为是。
馁只是体不充而欿然之谓。上下馁字。只是一意。而非谓气馁。亦非谓道义馁也。无是馁也。谓无气则人之行不能勇决充极也。饶说固强分。而程朱何尝有气馁道义馁之意耶。
气配道义而行则道义乃气之益也。犹人之为学而赖师友之益也。气乃集义而生则气者义之力也。犹人之有事功则有馀烈之可记述者也。
为说并恐苟且牵合。只可曰道义者。气之主。气者道义之资。其云气之益。尤似倒说。馀烈可述。意类无当。惟所云气者义之力。颇道得著。
浩气本是心中固有之物。善养以复其初则其为气之至大者道也。所谓体也。至刚者义也。所谓用也。气与道义合而言之则互为体用。气或为道义之体。如饶氏所谓论其用则道义非气无以行是也。道义或为气之体。如饶氏所谓论其体则气非道义。无以生是也如何。
浩气是人得天地正通之气遍体充满者。非必专指心中之气也。以气之至大者为道。至刚者为义。又似认气以为理。且气与道义之互为体用。说得可骇。大非贤者平日见识。况以己意驱率饶氏之言。要作我注脚耶。气与道义。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初无理体气用或气体理用。而体用成两截者也。幸更思之如何。
朱子曰告子直是将义屏除去。只就心上理会。窃疑若就此心上讲解理会许多理义。则有甚告子义外之患哉。若如陆子静不讲书不求理义。只静坐澄心。则是禅家之将敬字扫除而反观求心也。此告子之将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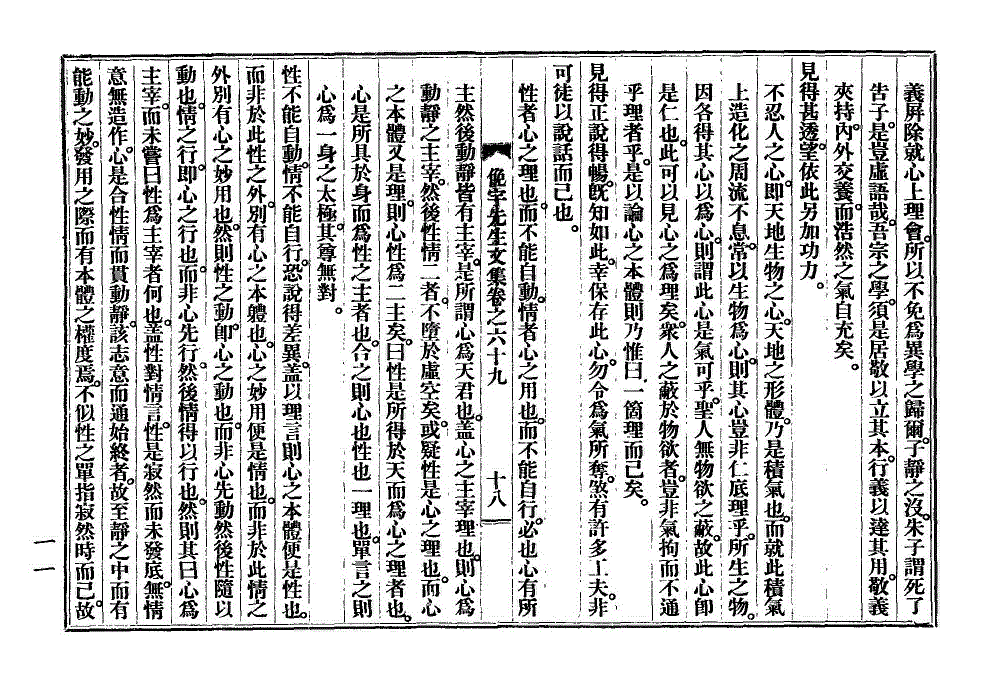 义屏除就心上理会。所以不免为异学之归尔。子静之没。朱子谓死了告子。是岂虚语哉。吾宗之学。须是居敬以立其本。行义以达其用。敬义夹持。内外交养。而浩然之气自充矣。
义屏除就心上理会。所以不免为异学之归尔。子静之没。朱子谓死了告子。是岂虚语哉。吾宗之学。须是居敬以立其本。行义以达其用。敬义夹持。内外交养。而浩然之气自充矣。见得甚透。望依此另加功力。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形体。乃是积气也。而就此积气上造化之周流不息。常以生物为心。则其心岂非仁底理乎。所生之物。因各得其心以为心。则谓此心是气可乎。圣人无物欲之蔽。故此心即是仁也。此可以见心之为理矣。众人之蔽于物欲者。岂非气拘而不通乎理者乎。是以论心之本体则乃惟曰一个理而已矣。
见得正说得畅。既知如此。幸保存此心。勿令为气所夺。煞有许多工夫。非可徒以说话而已也。
性者心之理也。而不能自动。情者心之用也。而不能自行。必也心有所主然后动静皆有主宰。是所谓心为天君也。盖心之主宰理也。则心为动静之主宰。然后性情二者。不堕于虚空矣。或疑性是心之理也。而心之本体又是理。则心性为二主矣。曰性是所得于天而为心之理者也。心是所具于身而为性之主者也。合之则心也性也一理也。单言之则心为一身之太极。其尊无对。
性不能自动。情不能自行。恐说得差异。盖以理言则心之本体便是性也。而非于此性之外。别有心之本体也。心之妙用便是情也。而非于此情之外别有心之妙用也。然则性之动。即心之动也。而非心先动然后性随以动也。情之行。即心之行也。而非心先行。然后情得以行也。然则其曰心为主宰。而未尝曰性为主宰者何也。盖性对情言。性是寂然而未发底。无情意无造作。心是合性情而贯动静。该志意而通始终者。故至静之中而有能动之妙。发用之际而有本体之权度焉。不似性之单指寂然时而已。故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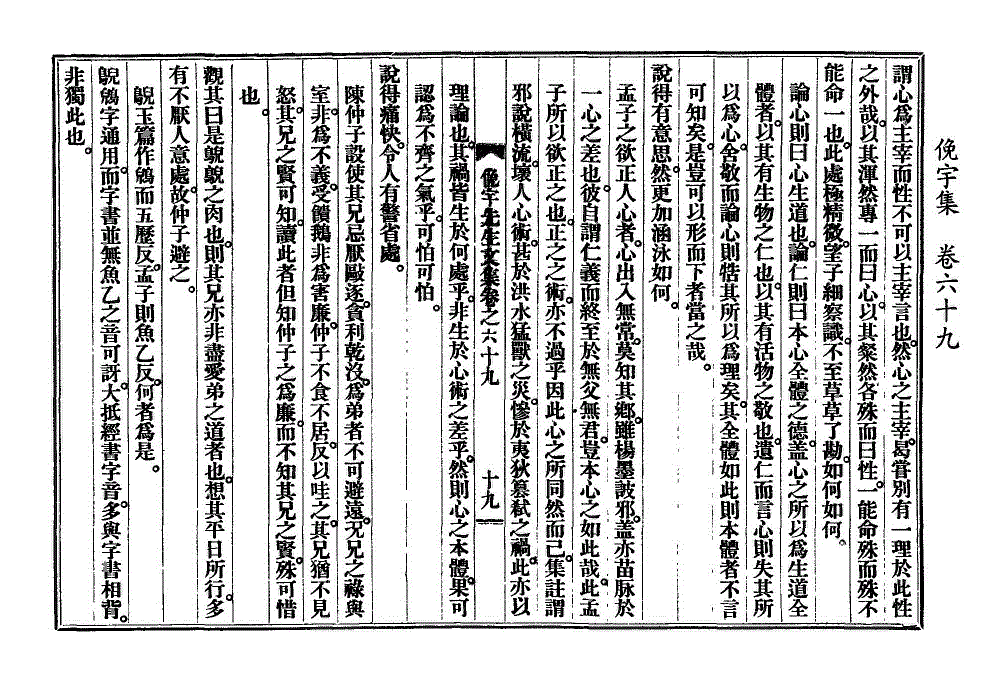 谓心为主宰而性不可以主宰言也。然心之主宰。曷尝别有一理于此性之外哉。以其浑然专一而曰心。以其粲然各殊而曰性。一能命殊而殊不能命一也。此处极精微。望子细察识。不至草草了勘。如何如何。
谓心为主宰而性不可以主宰言也。然心之主宰。曷尝别有一理于此性之外哉。以其浑然专一而曰心。以其粲然各殊而曰性。一能命殊而殊不能命一也。此处极精微。望子细察识。不至草草了勘。如何如何。论心则曰心生道也。论仁则曰本心全体之德。盖心之所以为生道全体者。以其有生物之仁也。以其有活物之敬也。遗仁而言心则失其所以为心。舍敬而论心则牿其所以为理矣。其全体如此则本体者不言可知矣。是岂可以形而下者当之哉。
说得有意思。然更加涵泳如何。
孟子之欲正人心者。心出入无常。莫知其乡。虽杨墨诐邪。盖亦苗脉于一心之差也。彼自谓仁义而终至于无父无君。岂本心之如此哉。此孟子所以欲正之也。正之之术。亦不过乎因此心之所同然而已。集注谓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此亦以理论也。其祸皆生于何处乎。非生于心术之差乎。然则心之本体。果可认为不齐之气乎。可怕可怕。
说得痛快。令人有警省处。
陈仲子设使其兄忌厌驱逐。贪利乾没。为弟者不可避远。况兄之禄与室。非为不义。受馈鹅非为害廉。仲子不食不居。反以哇之。其兄犹不见怒。其兄之贤可知。读此者但知仲子之为廉。而不知其兄之贤。殊可惜也。
观其曰是鹢鹢之肉也。则其兄亦非尽爱弟之道者也。想其平日所行。多有不厌人意处。故仲子避之。
鹢玉篇作鹢而五历反。孟子则鱼乙反。何者为是。
鹢鹢字通用。而字书并无鱼乙之音可讶。大抵经书字音。多与字书相背。非独此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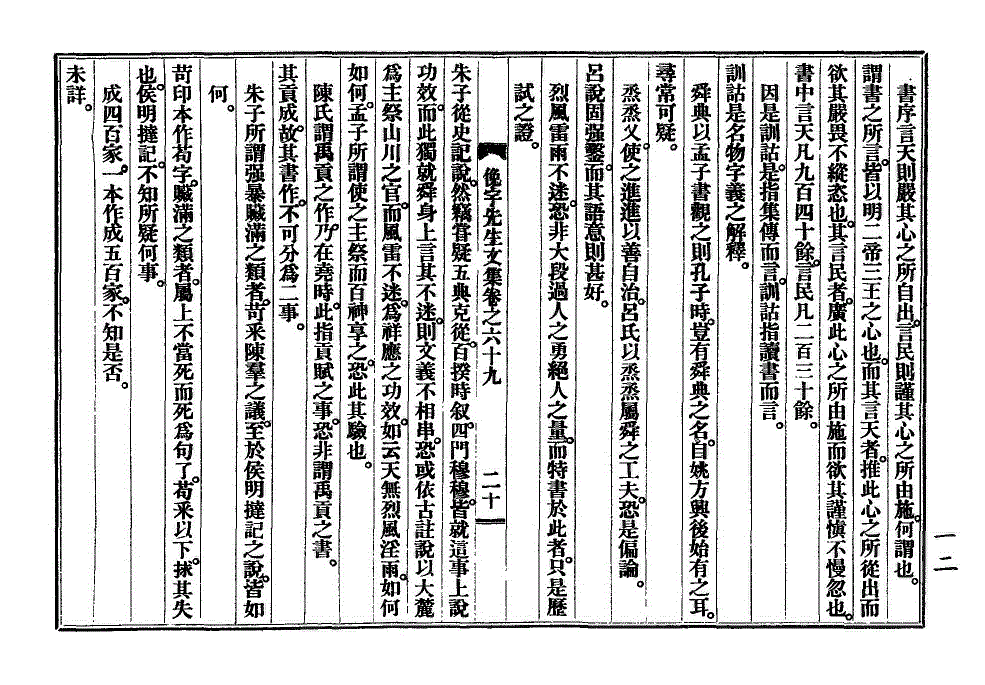 书序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何谓也。
书序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何谓也。谓书之所言。皆以明二帝三王之心也。而其言天者。推此心之所从出而欲其严畏不纵恣也。其言民者。广此心之所由施而欲其谨慎不慢忽也。书中言天凡九百四十馀。言民凡二百三十馀。
因是训诂。是指集传而言。训诂指读书而言。
训诂是名物字义之解释。
舜典以孟子书观之则孔子时。岂有舜典之名。自姚方兴后始有之耳。
寻常可疑。
烝烝乂。使之进进以善自治。吕氏以烝烝属舜之工夫。恐是偏论。
吕说固强凿。而其语意则甚好。
烈风雷雨不迷。恐非大段过人之勇绝人之量。而特书于此者。只是历试之證。
朱子从史记说。然窃尝疑五典克从。百揆时叙。四门穆穆。皆就这事上说功效。而此独就舜身上言其不迷。则文义不相串。恐或依古注说以大麓为主祭山川之官。而风雷不迷。为祥应之功效。如云天无烈风淫雨。如何如何。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恐此其验也。
陈氏谓禹贡之作。乃在尧时。此指贡赋之事。恐非谓禹贡之书。
其贡成。故其书作。不可分为二事。
朱子所谓强暴赃满之类者。苛(一作苟)采陈群之议。至于侯明挞记之说。皆如何。
苛印本作苟字。赃满之类者。属上不当死而死为句了。苟采以下。救其失也。侯明挞记。不知所疑何事。
成四百家。一本作成五百家。不知是否。
未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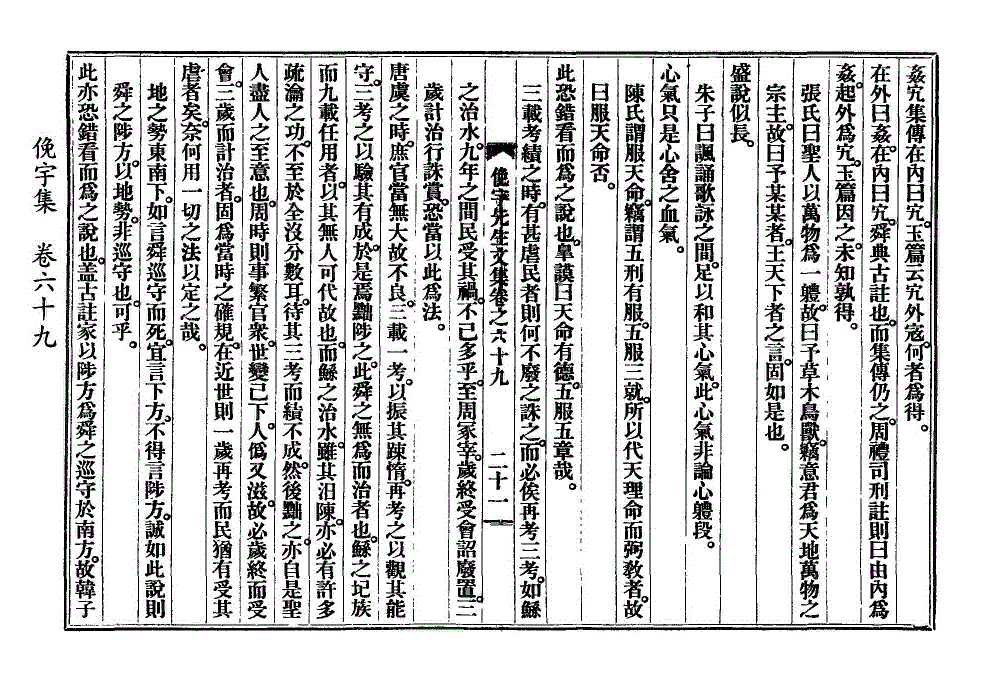 奸宄集传在内曰宄。玉篇云宄外寇。何者为得。
奸宄集传在内曰宄。玉篇云宄外寇。何者为得。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舜典古注也。而集传仍之。周礼司刑注则曰由内为奸。起外为宄。玉篇因之。未知孰得。
张氏曰圣人以万物为一体。故曰予草木鸟兽。窃意君为天地万物之宗主。故曰予某某者。王天下者之言。固如是也。
盛说似长。
朱子曰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此心气非论心体段。
心气只是心舍之血气。
陈氏谓服天命。窃谓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所以代天理命而弼教者。故曰服天命否。
此恐错看而为之说也。皋谟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三载考绩之时。有甚虐民者则何不废之诛之。而必俟再考三考。如鲧之治水。九年之间民受其祸。不已多乎。至周冢宰。岁终受会诏废置。三岁计治行诛赏。恐当以此为法。
唐虞之时。庶官当无大故不良。三载一考。以振其疏惰。再考之以观其能守。三考之以验其有成。于是焉黜陟之。此舜之无为而治者也。鲧之圮族而九载任用者。以其无人可代故也。而鲧之治水。虽其汩陈。亦必有许多疏瀹之功。不至于全没分数耳。待其三考而绩不成。然后黜之。亦自是圣人尽人之至意也。周时则事繁官众。世变已下。人伪又滋。故必岁终而受会。三岁而计治者。固为当时之确规。在近世则一岁再考而民犹有受其虐者矣。奈何用一切之法以定之哉。
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诚如此说则舜之陟方。以地势。非巡守也。可乎。
此亦恐错看而为之说也。盖古注家以陟方为舜之巡守于南方。故韩子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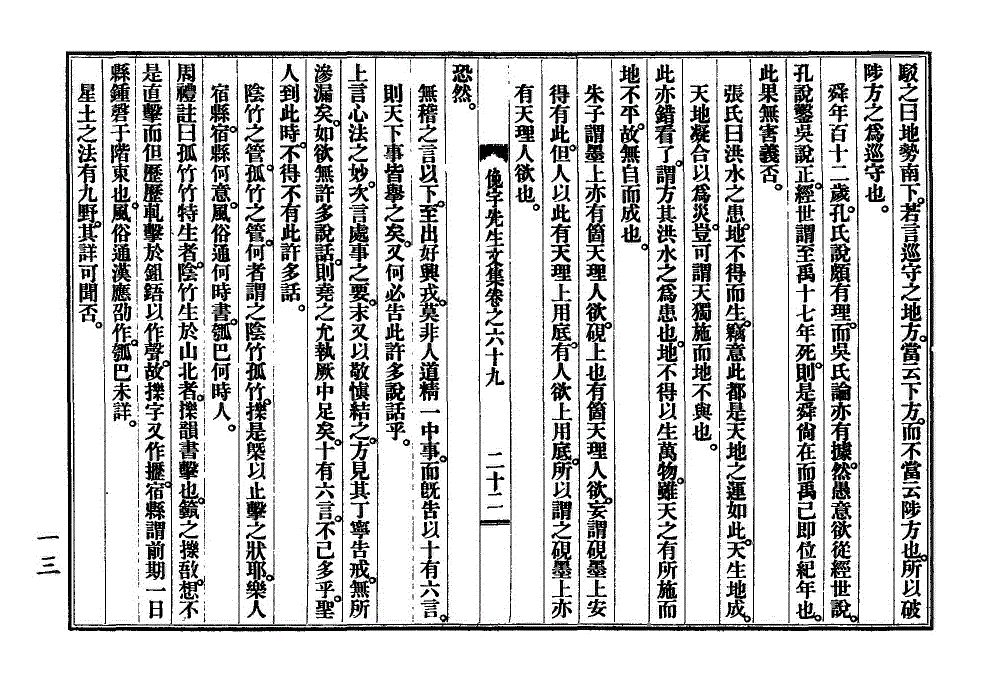 驳之曰地势南下。若言巡守之地方。当云下方。而不当云陟方也。所以破陟方之为巡守也。
驳之曰地势南下。若言巡守之地方。当云下方。而不当云陟方也。所以破陟方之为巡守也。舜年百十二岁。孔氏说颇有理。而吴氏论亦有据。然愚意欲从经世说。
孔说凿吴说正。经世谓至禹十七年死。则是舜尚在而禹已即位纪年也。此果无害义否。
张氏曰洪水之患。地不得而生。窃意此都是天地之运如此。天生地成。天地凝合以为灾。岂可谓天独施而地不与也。
此亦错看了。谓方其洪水之为患也。地不得以生万物。虽天之有所施而地不平。故无自而成也。
朱子谓墨上亦有个天理人欲。砚上也有个天理人欲。妄谓砚墨上安得有此。但人以此有天理上用底。有人欲上用底。所以谓之砚墨上亦有天理人欲也。
恐然。
无稽之言以下。至出好兴戎。莫非人道精一中事。而既告以十有六言。则天下事皆举之矣。又何必告此许多说话乎。
上言心法之妙。次言处事之要。末又以敬慎结之。方见其丁宁告戒。无所渗漏矣。如欲无许多说话。则尧之允执厥中足矣。十有六言。不已多乎。圣人到此时。不得不有此许多话。
阴竹之管。孤竹之管。何者谓之阴竹孤竹。擽是槩以止击之状耶。乐人宿县。宿县何意。风俗通何时书。瓠巴何时人。
周礼注曰孤竹竹特生者。阴竹生于山北者。擽韵书击也。籈之擽敔。想不是直击而但历历轧击于锄铻以作声。故擽字又作擽。宿县谓前期一日县钟磬于阶东也。风俗通汉应劭作。瓠巴未详。
星土之法有九野。其详可闻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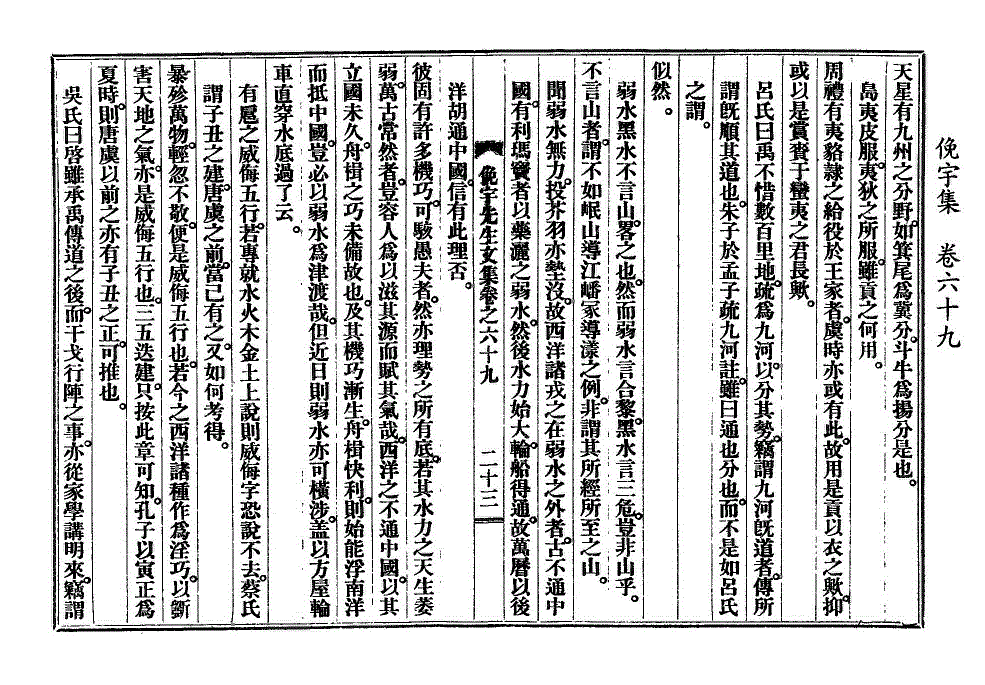 天星有九州之分野。如箕尾为冀分。斗牛为扬分是也。
天星有九州之分野。如箕尾为冀分。斗牛为扬分是也。岛夷皮服。夷狄之所服。虽贡之何用。
周礼有夷貉隶之给役于王家者。虞时亦或有此。故用是贡以衣之欤。抑或以是赏赉于蛮夷之君长欤。
吕氏曰禹不惜数百里地。疏为九河。以分其势。窃谓九河既道者。传所谓既顺其道也。朱子于孟子疏九河注。虽曰通也分也。而不是如吕氏之谓。
似然。
弱水黑水不言山。略之也。然而弱水言合黎。黑水言三危。岂非山乎。
不言山者。谓不如岷山导江嶓冢导漾之例。非谓其所经所至之山。
闻弱水无力。投芥羽亦垫没。故西洋诸戎之在弱水之外者。古不通中国。有利玛窦者以药洒之弱水。然后水力始大。轮船得通。故万历以后洋胡通中国。信有此理否。
彼固有许多机巧。可骇愚夫者。然亦理势之所有底。若其水力之天生萎弱。万古常然者。岂容人为以滋其源而赋其气哉。西洋之不通中国。以其立国未久。舟楫之巧未备故也。及其机巧渐生。舟楫快利。则始能浮南洋而抵中国。岂必以弱水为津渡哉。但近日则弱水亦可横涉。盖以方屋轮车直穿水底过了云。
有扈之威侮五行。若专就水火木金土上说则威侮字恐说不去。蔡氏谓子丑之建。唐虞之前。当已有之。又如何考得。
暴殄万物。轻忽不敬。便是威侮五行也。若今之西洋诸种作为淫巧。以斲害天地之气。亦是威侮五行也。三五迭建。只按此章可知。孔子以寅正为夏时。则唐虞以前之亦有子丑之正。可推也。
吴氏曰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阵之事。亦从家学讲明来。窃谓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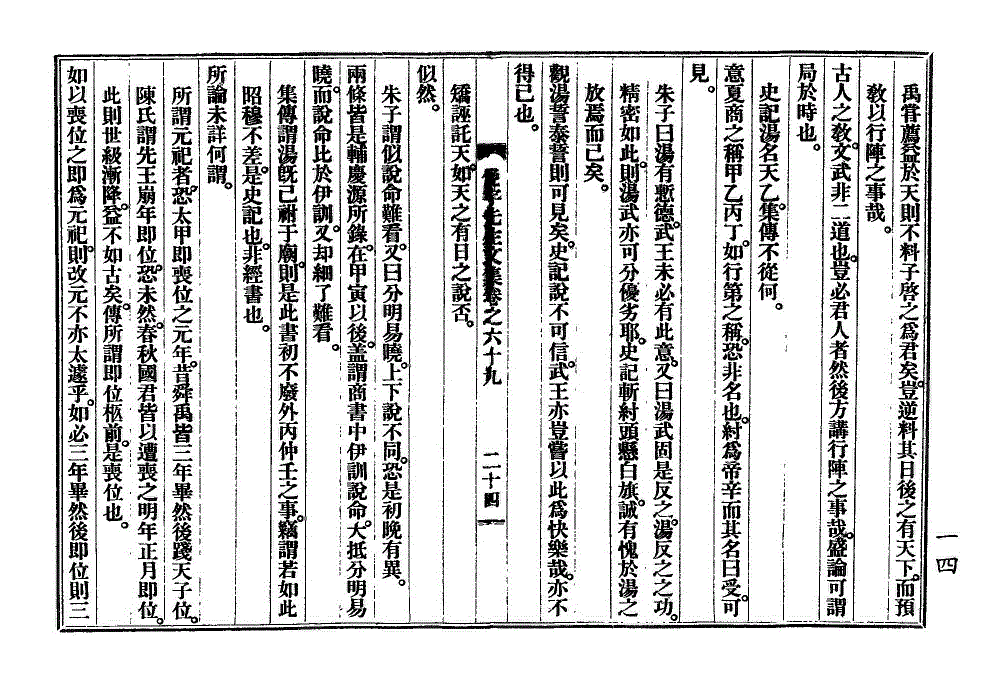 禹尝荐益于天则不料子启之为君矣。岂逆料其日后之有天下。而预教以行阵之事哉。
禹尝荐益于天则不料子启之为君矣。岂逆料其日后之有天下。而预教以行阵之事哉。古人之教。文武非二道也。岂必君人者然后方讲行阵之事哉。盛论可谓局于时也。
史记汤名天乙。集传不从何。
意夏商之称甲乙丙丁。如行第之称。恐非名也。纣为帝辛而其名曰受。可见。
朱子曰汤有惭德。武王未必有此意。又曰汤武固是反之。汤反之之功。精密如此。则汤武亦可分优劣耶。史记斩纣头悬白旗。诚有愧于汤之放焉而已矣。
观汤誓泰誓则可见矣。史记说不可信。武王亦岂尝以此为快乐哉。亦不得已也。
矫诬托天。如天之有日之说否。
似然。
朱子谓似说命难看。又曰分明易晓。上下说不同。恐是初晚有异。
两条皆是辅庆源所录。在甲寅以后。盖谓商书中伊训说命。大抵分明易晓。而说命比于伊训。又却细了难看。
集传谓汤既已祔于庙。则是此书初不废外丙仲壬之事。窃谓若如此昭穆不差。是史记也。非经书也。
所论未详何谓。
所谓元祀者。恐太甲即丧位之元年。昔舜禹皆三年毕然后践天子位。陈氏谓先王崩年即位。恐未然。春秋国君皆以遭丧之明年正月即位。此则世级渐降。益不如古矣。传所谓即位柩前。是丧位也。
如以丧位之即为元祀。则改元不亦太遽乎。如必三年毕然后即位则三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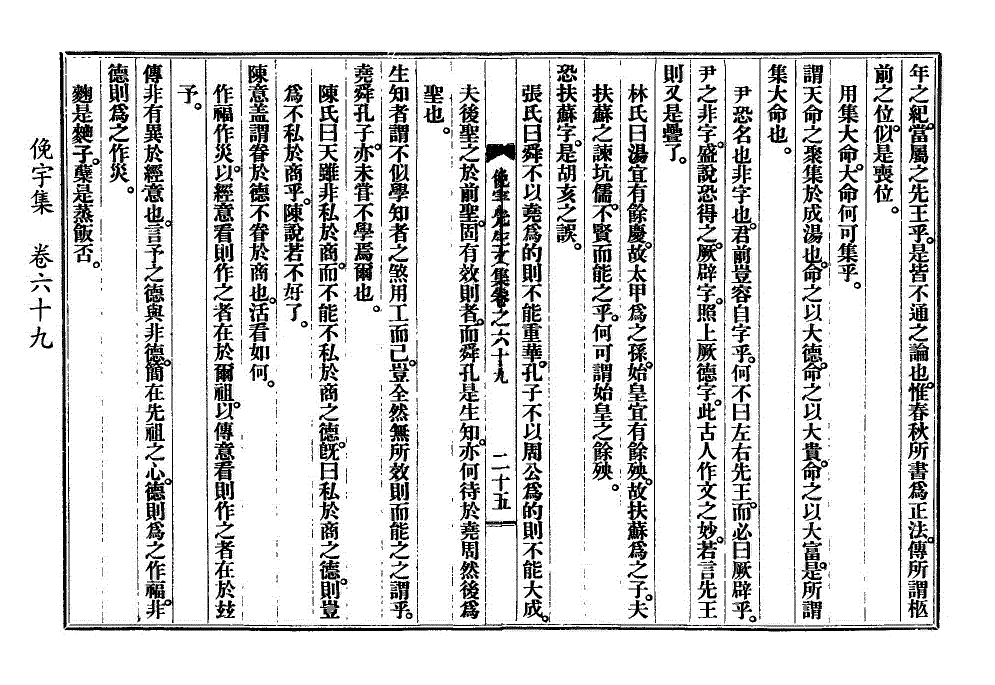 年之纪。当属之先王乎。是皆不通之论也。惟春秋所书为正法。传所谓柩前之位。似是丧位。
年之纪。当属之先王乎。是皆不通之论也。惟春秋所书为正法。传所谓柩前之位。似是丧位。用集大命。大命何可集乎。
谓天命之聚集于成汤也。命之以大德。命之以大贵。命之以大富。是所谓集大命也。
尹恐名也非字也。君前岂容自字乎。何不曰左右先王。而必曰厥辟乎。
尹之非字。盛说恐得之。厥辟字。照上厥德字。此古人作文之妙。若言先王则又是叠了。
林氏曰汤宜有馀庆。故太甲为之孙。始皇宜有馀殃。故扶苏为之子。夫扶苏之谏坑儒。不贤而能之乎。何可谓始皇之馀殃。
恐扶苏字。是胡亥之误。
张氏曰舜不以尧为的则不能重华。孔子不以周公为的则不能大成。夫后圣之于前圣。固有效则者。而舜孔是生知。亦何待于尧周然后为圣也。
生知者谓不似学知者之煞用工而已。岂全然无所效则而能之之谓乎。尧舜孔子。亦未尝不学焉尔也。
陈氏曰天虽非私于商。而不能不私于商之德。既曰私于商之德。则岂为不私于商乎。陈说若不好了。
陈意盖谓眷于德不眷于商也。活看如何。
作福作灾。以经意看则作之者在于尔祖。以传意看则作之者在于玆予。
传非有异于经意也。言予之德与非德。简在先祖之心。德则为之作福。非德则为之作灾。
曲是曲子。蘖是蒸饭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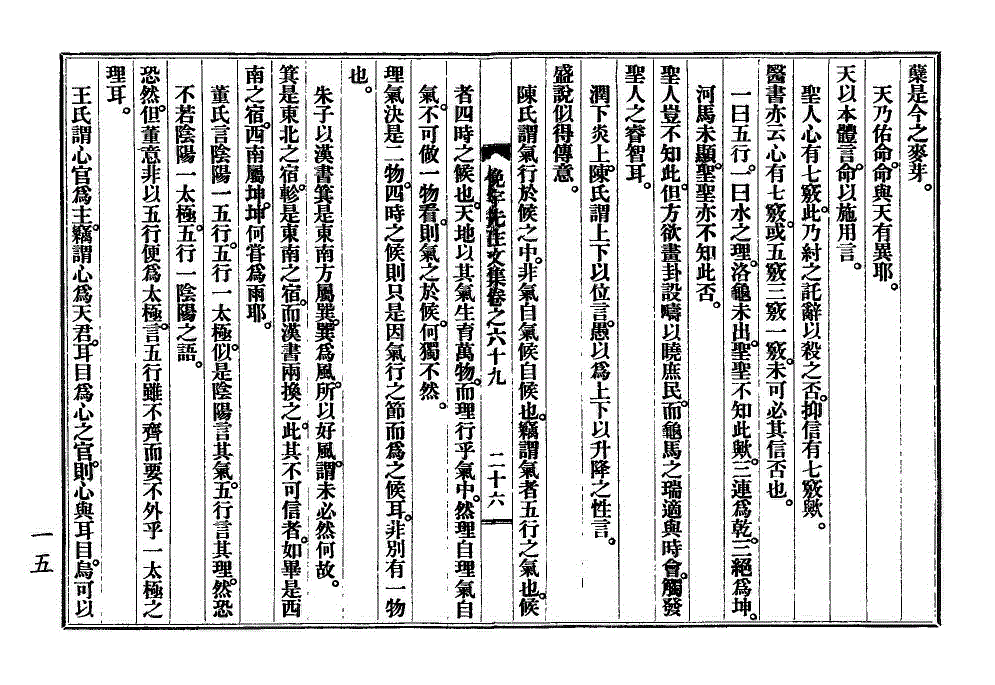 蘖是今之麦芽。
蘖是今之麦芽。天乃佑命。命与天有异耶。
天以本体言。命以施用言。
圣人心有七窍。此乃纣之托辞以杀之否。抑信有七窍欤。
医书亦云心有七窍。或五窍三窍一窍。未可必其信否也。
一曰五行。一曰水之理。洛龟未出。圣圣不知此欤。三连为乾。三绝为坤。河马未显。圣圣亦不知此否。
圣人岂不知此。但方欲画卦设畴以晓庶民。而龟马之瑞适与时会。触发圣人之睿智耳。
润下炎上。陈氏谓上下以位言。愚以为上下以升降之性言。
盛说似得传意。
陈氏谓气行于候之中。非气自气候自候也。窃谓气者五行之气也。候者四时之候也。天地以其气生育万物。而理行乎气中。然理自理气自气。不可做一物看。则气之于候。何独不然。
理气决是二物。四时之候则只是因气行之节而为之候耳。非别有一物也。
朱子以汉书箕是东南方属巽。巽为风。所以好风。谓未必然何故。
箕是东北之宿。轸是东南之宿。而汉书两换之。此其不可信者。如毕是西南之宿。西南属坤。坤何尝为雨耶。
董氏言阴阳一五行。五行一太极。似是阴阳言其气。五行言其理。然恐不若阴阳一太极。五行一阴阳之语。
恐然。但董意非以五行便为太极。言五行虽不齐而要不外乎一太极之理耳。
王氏谓心官为主。窃谓心为天君。耳目为心之官。则心与耳目。乌可以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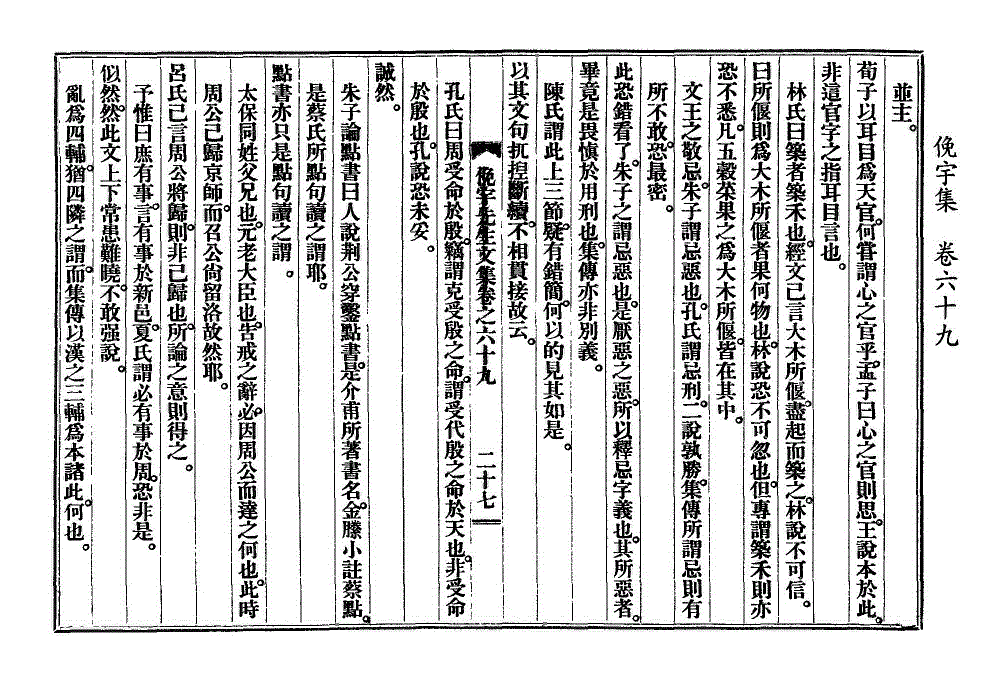 并主。
并主。荀子以耳目为天官。何尝谓心之官乎。孟子曰心之官则思。王说本于此。非这官字之指耳目言也。
林氏曰筑者筑禾也。经文已言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林说不可信。
曰所偃则为大木所偃者果何物也。林说恐不可忽也。但专谓筑禾则亦恐不悉。凡五谷菜果之为大木所偃。皆在其中。
文王之敬忌。朱子谓忌恶也。孔氏谓忌刑。二说孰胜。集传所谓忌则有所不敢。恐最密。
此恐错看了。朱子之谓忌恶也。是厌恶之恶。所以释忌字义也。其所恶者。毕竟是畏慎于用刑也。集传亦非别义。
陈氏谓此上三节。疑有错简。何以的见其如是。
以其文句扤捏断续。不相贯接故云。
孔氏曰周受命于殷。窃谓克受殷之命。谓受代殷之命于天也。非受命于殷也。孔说恐未妥。
诚然。
朱子论点书曰人说荆公穿凿点书。是介甫所著书名。金縢小注蔡点。是蔡氏所点句读之谓耶。
点书亦只是点句读之谓。
太保同姓父兄也。元老大臣也。告戒之辞。必因周公而达之何也。此时周公已归京师。而召公尚留洛故然耶。
吕氏已言周公将归。则非已归也。所论之意则得之。
予惟曰庶有事。言有事于新邑。夏氏谓必有事于周。恐非是。
似然。然此文上下常患难晓。不敢强说。
乱为四辅。犹四邻之谓。而集传以汉之三辅为本诸此。何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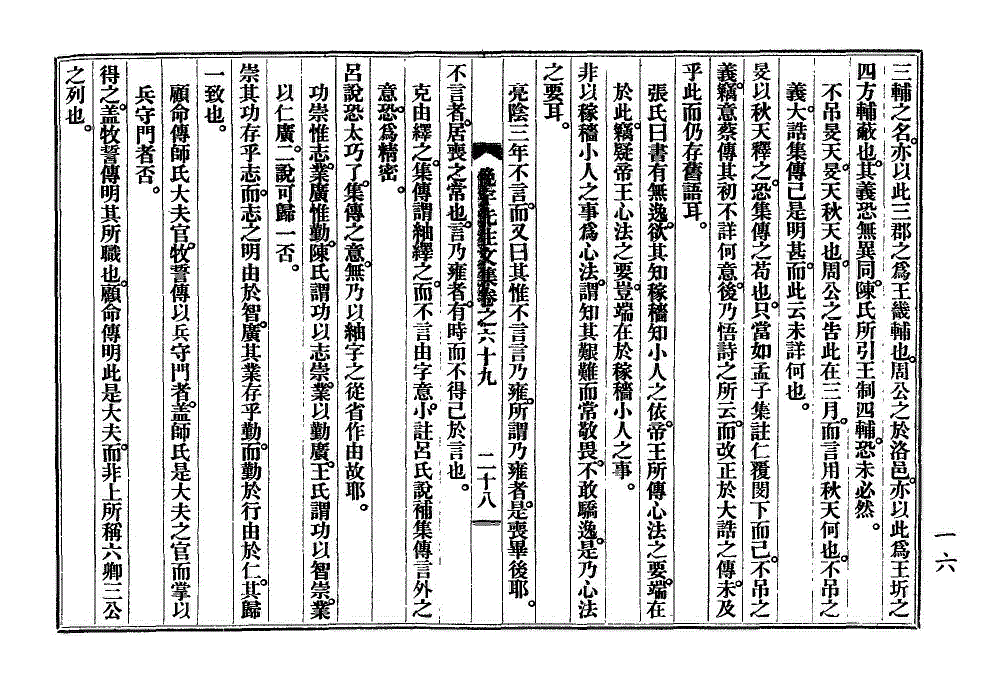 三辅之名。亦以此三郡之为王畿辅也。周公之于洛邑。亦以此为王圻之四方辅蔽也。其义恐无异同。陈氏所引王制四辅。恐未必然。
三辅之名。亦以此三郡之为王畿辅也。周公之于洛邑。亦以此为王圻之四方辅蔽也。其义恐无异同。陈氏所引王制四辅。恐未必然。不吊旻天。旻天秋天也。周公之告此在三月。而言用秋天何也。不吊之义。大诰集传已是明甚。而此云未详何也。
旻以秋天释之。恐集传之苟也。只当如孟子集注仁覆闵下而已。不吊之义。窃意蔡传其初不详何意。后乃悟诗之所云。而改正于大诰之传。未及乎此而仍存旧语耳。
张氏曰书有无逸。欲其知稼穑知小人之依。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于此。窃疑帝王心法之要。岂端在于稼穑小人之事。
非以稼穑小人之事为心法。谓知其艰难而常敬畏。不敢骄逸。是乃心法之要耳。
亮阴三年不言。而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所谓乃雍者。是丧毕后耶。
不言者。居丧之常也。言乃雍者。有时而不得已于言也。
克由绎之。集传谓䌷绎之。而不言由字意。小注吕氏说补集传言外之意。恐为精密。
吕说恐太巧了。集传之意。无乃以䌷字之从省作由故耶。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陈氏谓功以志崇。业以勤广。王氏谓功以智崇。业以仁广。二说可归一否。
崇其功存乎志。而志之明由于智。广其业存乎勤。而勤于行由于仁。其归一致也。
顾命传师氏大夫官。牧誓传以兵守门者。盖师氏是大夫之官而掌以兵守门者否。
得之。盖牧誓传明其所职也。顾命传明此是大夫。而非上所称六卿三公之列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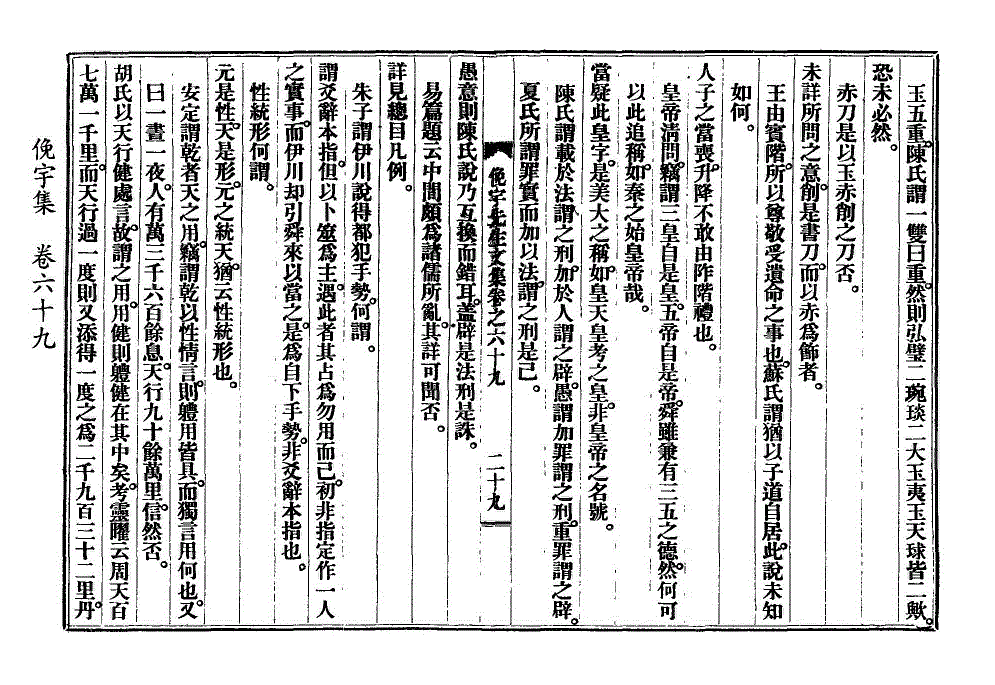 玉五重。陈氏谓一双曰重。然则弘璧二琬琰二大玉夷玉天球皆二欤。
玉五重。陈氏谓一双曰重。然则弘璧二琬琰二大玉夷玉天球皆二欤。恐未必然。
赤刀是以玉赤削之刀否。
未详所问之意。削是书刀。而以赤为饰者。
王由宾阶。所以尊敬受遗命之事也。苏氏谓犹以子道自居。此说未知如何。
人子之当丧。升降不敢由阼阶礼也。
皇帝清问。窃谓三皇自是皇。五帝自是帝。舜虽兼有三五之德。然何可以此追称。如秦之始皇帝哉。
当疑此皇字。是美大之称。如皇天皇考之皇。非皇帝之名号。
陈氏谓载于法谓之刑。加于人谓之辟。愚谓加罪谓之刑。重罪谓之辟。夏氏所谓罪实而加以法。谓之刑是已。
愚意则陈氏说乃互换而错耳。盖辟是法刑是诛。
易篇题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其详可闻否。
详见总目凡例。
朱子谓伊川说得都犯手势。何谓。
谓爻辞本指。但以卜筮为主。遇此者其占为勿用而已。初非指定作一人之实事。而伊川却引舜来以当之。是为自下手势。非爻辞本指也。
性统形何谓。
元是性。天是形。元之统天。犹云性统形也。
安定谓乾者天之用。窃谓乾以性情言。则体用皆具。而独言用何也。又曰一昼一夜。人有万三千六百馀息。天行九十馀万里。信然否。
胡氏以天行健处言。故谓之用。用健则体健在其中矣。考灵曜云周天百七万一千里。而天行过一度则又添得一度之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丹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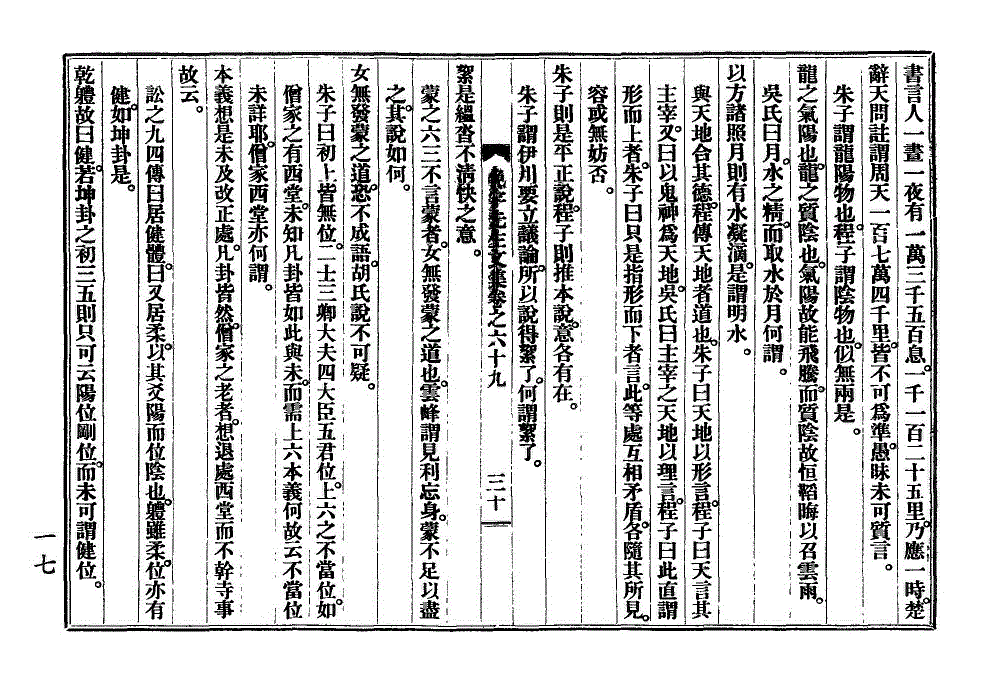 书言人一昼一夜有一万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里。乃应一时。楚辞天问注谓周天一百七万四千里。皆不可为准。愚昧未可质言。
书言人一昼一夜有一万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里。乃应一时。楚辞天问注谓周天一百七万四千里。皆不可为准。愚昧未可质言。朱子谓龙阳物也。程子谓阴物也。似无两是。
龙之气阳也。龙之质阴也。气阳故能飞腾。而质阴故恒韬晦以召云雨。
吴氏曰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何谓。
以方诸照月则有水凝滴。是谓明水。
与天地合其德。程传天地者道也。朱子曰天地以形言。程子曰天言其主宰。又曰以鬼神为天地。吴氏曰主宰之天地以理言。程子曰此直谓形而上者。朱子曰只是指形而下者言。此等处互相矛盾。各随其所见。容或无妨否。
朱子则是平正说。程子则推本说。意各有在。
朱子谓伊川要立议论。所以说得絮了。何谓絮了。
絮是缊沓不清快之意。
蒙之六三不言蒙者。女无发蒙之道也。云峰谓见利忘身。蒙不足以尽之。其说如何。
女无发蒙之道。恐不成语。胡氏说不可疑。
朱子曰初上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当位。如僧家之有西堂。未知凡卦皆如此与未。而需上六本义何故云不当位未详耶。僧家西堂亦何谓。
本义想是未及改正处。凡卦皆然。僧家之老者。想退处西堂而不干寺事故云。
讼之九四传曰居健体。曰又居柔。以其爻阳而位阴也。体虽柔。位亦有健。如坤卦是。
乾体故曰健。若坤卦之初三五则只可云阳位刚位。而未可谓健位。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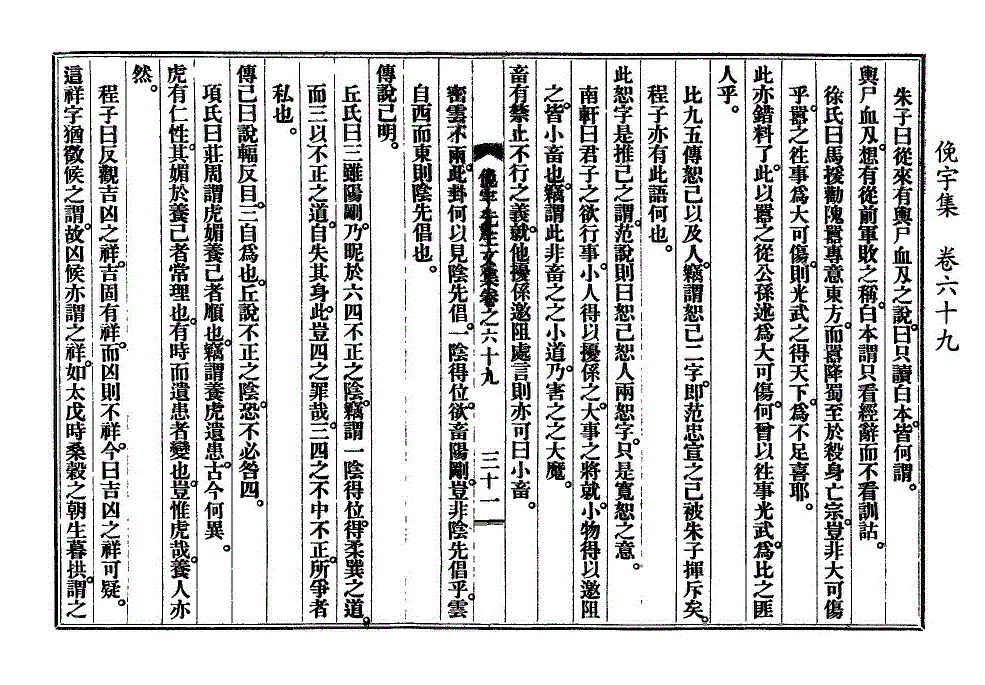 朱子曰从来有舆尸血刃之说。曰只读白本。皆何谓。
朱子曰从来有舆尸血刃之说。曰只读白本。皆何谓。舆尸血刃。想有从前军败之称。白本谓只看经辞而不看训诂。
徐氏曰马援劝隗嚣专意东方。而嚣降蜀至于杀身亡宗。岂非大可伤乎。嚣之往事为大可伤。则光武之得天下。为不足喜耶。
此亦错料了。此以嚣之从公孙述为大可伤。何曾以往事光武。为比之匪人乎。
比九五传恕己以及人。窃谓恕己二字。即范忠宣之己被朱子挥斥矣。程子亦有此语何也。
此恕字是推己之谓。范说则曰恕己恕人两恕字。只是宽恕之意。
南轩曰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扰系之。大事之将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窃谓此非畜之之小道。乃害之之大魔。
畜有禁止不行之义。就他扰系邀阻处言则亦可曰小畜。
密云不雨。此卦何以见阴先倡。一阴得位。欲畜阳刚。岂非阴先倡乎。云自西而东则阴先倡也。
传说已明。
丘氏曰三虽阳刚。乃昵于六四不正之阴。窃谓一阴得位。得柔巽之道。而三以不正之道。自失其身。此岂四之罪哉。三四之不中不正。所争者私也。
传已曰说辐反目。三自为也。丘说不正之阴。恐不必咎四。
项氏曰庄周谓虎媚养己者顺也。窃谓养虎遗患。古今何异。
虎有仁性。其媚于养己者常理也。有时而遗患者变也。岂惟虎哉。养人亦然。
程子曰反观吉凶之祥。吉固有祥。而凶则不祥。今曰吉凶之祥可疑。
这祥字犹徵候之谓。故凶候亦谓之祥。如太戊时桑谷之朝生暮拱。谓之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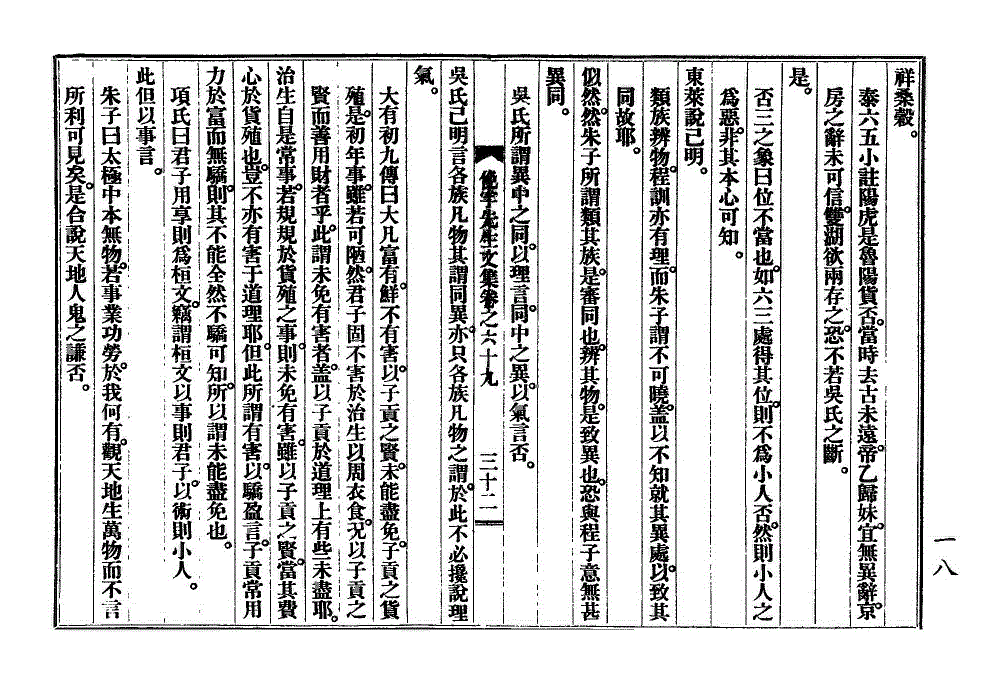 祥桑谷。
祥桑谷。泰六五小注阳虎是鲁阳货否。当时去古未远。帝乙归妹。宜无异辞。京房之辞未可信。双湖欲两存之。恐不若吴氏之断。
是。
否三之象曰位不当也。如六三处得其位。则不为小人否。然则小人之为恶。非其本心可知。
东莱说已明。
类族辨物。程训亦有理。而朱子谓不可晓。盖以不知就其异处。以致其同故耶。
似然。然朱子所谓类其族。是审同也。辨其物。是致异也。恐与程子意无甚异同。
吴氏所谓异中之同。以理言。同中之异。以气言否。
吴氏已明言各族凡物其谓同异。亦只各族凡物之谓。于此不必搀说理气。
大有初九传曰大凡富有。鲜不有害。以子贡之贤。未能尽免。子贡之货殖。是初年事。虽若可陋。然君子固不害于治生以周衣食。况以子贡之贤而善用财者乎。此谓未免有害者。盖以子贡于道理上有些未尽耶。
治生自是常事。若规规于货殖之事。则未免有害。虽以子贡之贤。当其费心于货殖也。岂不亦有害于道理耶。但此所谓有害。以骄盈言。子贡常用力于富而无骄。则其不能全然不骄可知。所以谓未能尽免也。
项氏曰君子用享则为桓文。窃谓桓文以事则君子。以术则小人。
此但以事言。
朱子曰太极中本无物。若事业功劳。于我何有。观天地生万物而不言所利可见矣。是合说天地人鬼之谦否。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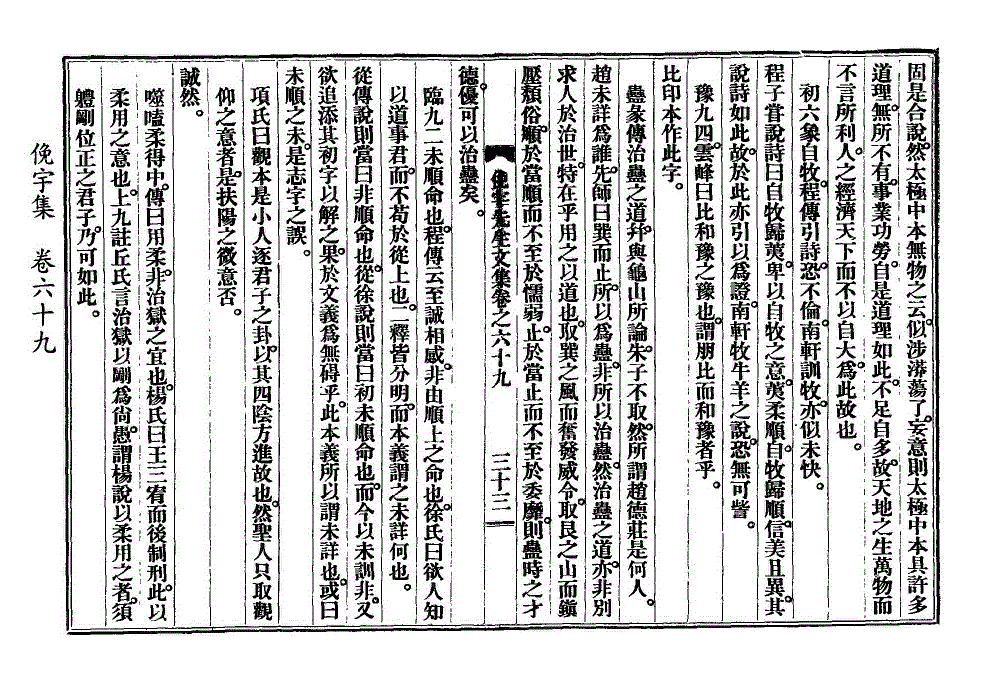 固是合说。然太极中本无物之云。似涉漭荡了。妄意则太极中本具许多道理。无所不有。事业功劳。自是道理如此。不足自多。故天地之生万物而不言所利。人之经济天下而不以自大。为此故也。
固是合说。然太极中本无物之云。似涉漭荡了。妄意则太极中本具许多道理。无所不有。事业功劳。自是道理如此。不足自多。故天地之生万物而不言所利。人之经济天下而不以自大。为此故也。初六象自牧。程传引诗。恐不伦。南轩训牧。亦似未快。
程子尝说诗曰自牧归荑。卑以自牧之意。荑柔顺。自牧归顺。信美且异。其说诗如此。故于此亦引以为證。南轩牧牛羊之说。恐无可訾。
豫九四。云峰曰比和豫之豫也。谓朋比而和豫者乎。
比印本作此字。
蛊彖传治蛊之道。并与龟山所论。朱子不取。然所谓赵德庄是何人。
赵未详为谁。先师曰巽而止。所以为蛊。非所以治蛊。然治蛊之道。亦非别求人于治世。特在乎用之以道也。取巽之风而奋发威令。取艮之山而镇压颓俗。顺于当顺而不至于懦弱。止于当止而不至于委靡。则蛊时之才德。优可以治蛊矣。
临九二未顺命也。程传云至诚相感。非由顺上之命也。徐氏曰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于从上也。二释皆分明。而本义谓之未详何也。
从传说则当曰非顺命也。从徐说则当曰初未顺命也。而今以未训非。又欲追添其初字以解之。果于文义为无碍乎。此本义所以谓未详也。或曰未顺之未。是志字之误。
项氏曰观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以其四阴方进故也。然圣人只取观仰之意者。是扶阳之微意否。
诚然。
噬嗑柔得中。传曰用柔。非治狱之宜也。杨氏曰王三宥而后制刑。此以柔用之意也。上九注丘氏言治狱以刚为尚。愚谓杨说以柔用之者。须体刚位正之君子。乃可如此。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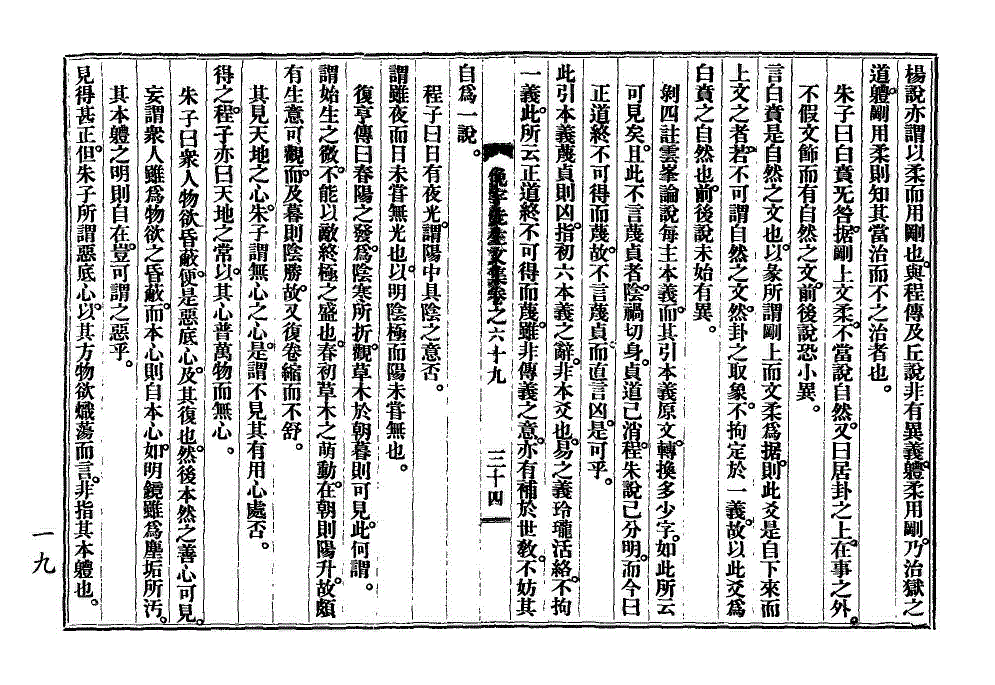 杨说亦谓以柔而用刚也。与程传及丘说非有异义。体柔用刚。乃治狱之道。体刚用柔则知其当治而不之治者也。
杨说亦谓以柔而用刚也。与程传及丘说非有异义。体柔用刚。乃治狱之道。体刚用柔则知其当治而不之治者也。朱子曰白贲无咎。据刚上文柔。不当说自然。又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饰而有自然之文。前后说恐小异。
言白贲是自然之文也。以彖所谓刚上而文柔为据。则此爻是自下来而上文之者。若不可谓自然之文。然卦之取象。不拘定于一义。故以此爻为白贲之自然也。前后说未始有异。
剥四注云峰论说每主本义。而其引本义原文。转换多少字。如此所云可见矣。且此不言蔑贞者。阴祸切身。贞道已消。程朱说已分明。而今曰正道终不可得而蔑。故不言蔑贞。而直言凶。是可乎。
此引本义蔑贞则凶。指初六本义之辞。非本爻也。易之义玲珑活络。不拘一义。此所云正道终不可得而蔑。虽非传义之意。亦有补于世教。不妨其自为一说。
程子曰日有夜光。谓阳中具阴之意否。
谓虽夜而日未尝无光也。以明阴极而阳未尝无也。
复亨传曰春阳之发。为阴寒所折。观草木于朝暮则可见。此何谓。
谓始生之微。不能以敌终极之盛也。春初草木之萌动。在朝则阳升。故颇有生意可观。而及暮则阴胜。故又复卷缩而不舒。
其见天地之心。朱子谓无心之心。是谓不见其有用心处否。
得之。程子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
朱子曰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及其复也。然后本然之善心可见。妄谓众人虽为物欲之昏蔽。而本心则自本心。如明镜虽为尘垢所污。其本体之明则自在。岂可谓之恶乎。
见得甚正。但朱子所谓恶底心。以其方物欲炽荡而言。非指其本体也。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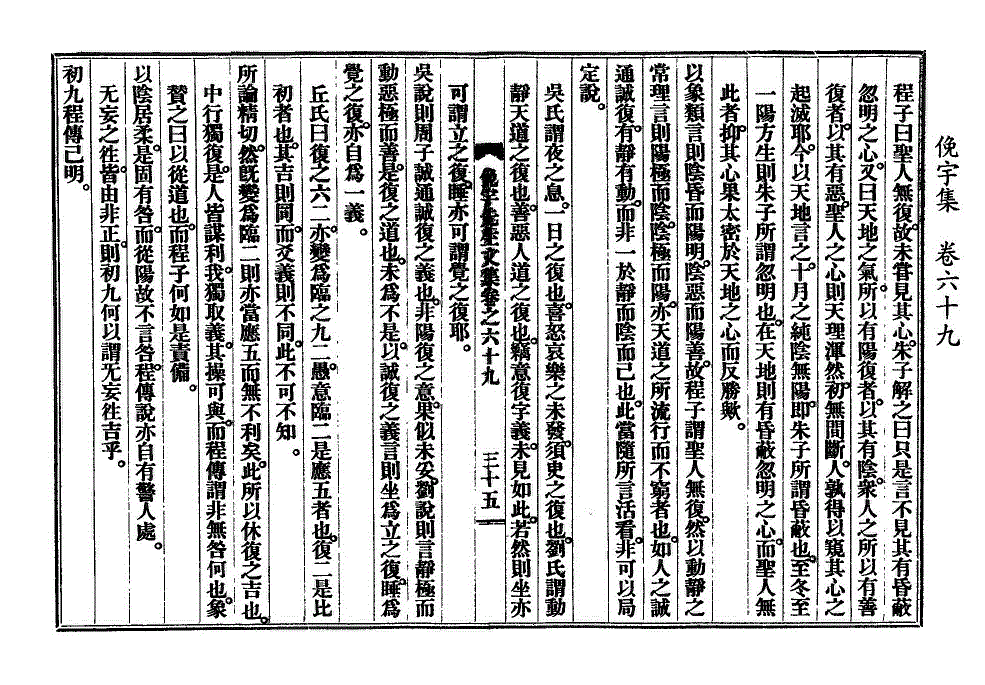 程子曰圣人无复。故未尝见其心。朱子解之曰只是言不见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又曰天地之气。所以有阳复者。以其有阴。众人之所以有善复者。以其有恶。圣人之心则天理浑然。初无间断。人孰得以窥其心之起灭耶。今以天地言之。十月之纯阴无阳。即朱子所谓昏蔽也。至冬至一阳方生则朱子所谓忽明也。在天地则有昏蔽忽明之心。而圣人无此者。抑其心果太密于天地之心而反胜欤。
程子曰圣人无复。故未尝见其心。朱子解之曰只是言不见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又曰天地之气。所以有阳复者。以其有阴。众人之所以有善复者。以其有恶。圣人之心则天理浑然。初无间断。人孰得以窥其心之起灭耶。今以天地言之。十月之纯阴无阳。即朱子所谓昏蔽也。至冬至一阳方生则朱子所谓忽明也。在天地则有昏蔽忽明之心。而圣人无此者。抑其心果太密于天地之心而反胜欤。以象类言则阴昏而阳明。阴恶而阳善。故程子谓圣人无复。然以动静之常理言则阳极而阴。阴极而阳。亦天道之所流行而不穷者也。如人之诚通诚复。有静有动。而非一于静而阴而已也。此当随所言活看。非可以局定说。
吴氏谓夜之息。一日之复也。喜怒哀乐之未发。须臾之复也。刘氏谓动静天道之复也。善恶人道之复也。窃意复字义。未见如此。若然则坐亦可谓立之复。睡亦可谓觉之复耶。
吴说则周子诚通诚复之义也。非阳复之意。果似未妥。刘说则言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是复之道也。未为不是。以诚复之义言则坐为立之复。睡为觉之复。亦自为一义。
丘氏曰复之六二。亦变为临之九二。愚意临二是应五者也。复二是比初者也。其吉则同。而爻义则不同。此不可不知。
所论精切。然既变为临二则亦当应五而无不利矣。此所以休复之吉也。
中行独复。是人皆谋利。我独取义。其操可与。而程传谓非无咎何也。象赞之曰以从道也。而程子何如是责备。
以阴居柔。是固有咎。而从阳故不言咎。程传说亦自有警人处。
无妄之往。皆由非正。则初九何以谓无妄往吉乎。
初九程传已明。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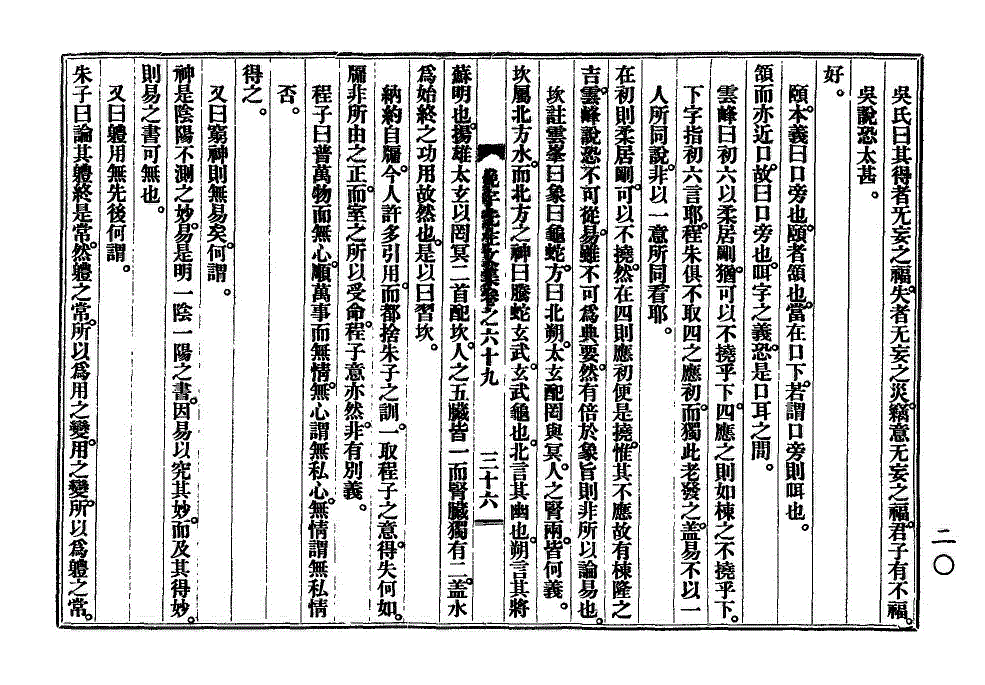 吴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失者无妄之灾。窃意无妄之福。君子有不福。吴说恐太甚。
吴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失者无妄之灾。窃意无妄之福。君子有不福。吴说恐太甚。好。
颐。本义曰口旁也。颐者颔也。当在口下。若谓口旁则咡也。
颔而亦近口。故曰口旁也。咡字之义。恐是口耳之间。
云峰曰初六以柔居刚。犹可以不挠乎下。四应之则如栋之不挠乎下。下字指初六言耶。程朱俱不取四之应初。而独此老发之。盖易不以一人所同说。非以一意所同看耶。
在初则柔居刚。可以不挠。然在四则应初便是挠。惟其不应故有栋隆之吉。云峰说恐不可从。易虽不可为典要。然有倍于象旨则非所以论易也。
坎注云峰曰象曰龟蛇。方曰北朔。太玄配罔与冥。人之肾两。皆何义。
坎属北方水。而北方之神曰腾蛇玄武。玄武龟也。北言其幽也。朔言其将苏明也。扬雄太玄以罔冥二首配坎。人之五脏皆一而肾脏独有二。盖水为始终之功用故然也。是以曰习坎。
纳约自牖。今人许多引用。而都舍朱子之训。一取程子之意。得失何如。
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命。程子意亦然。非有别义。
程子曰普万物而无心。顺万事而无情。无心谓无私心。无情谓无私情否。
得之。
又曰穷神则无易矣。何谓。
神是阴阳不测之妙。易是明一阴一阳之书。因易以究其妙。而及其得妙。则易之书可无也。
又曰体用无先后何谓。
朱子曰论其体终是常。然体之常。所以为用之变。用之变。所以为体之常。
俛宇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第 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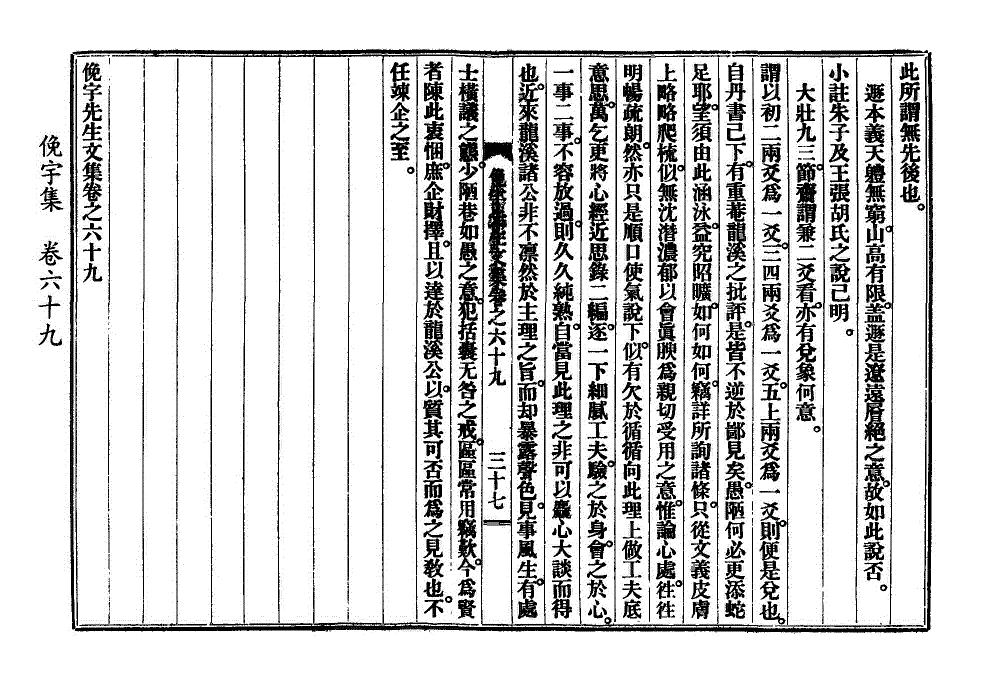 此所谓无先后也。
此所谓无先后也。遁本义天体无穷。山高有限。盖遁是辽远层绝之意。故如此说否。
小注朱子及王张胡氏之说已明。
大壮九三。节斋谓兼二爻看。亦有兑象何意。
谓以初二两爻为一爻。三四两爻为一爻。五上两爻为一爻。则便是兑也。自丹书已下。有重庵龙溪之批评。是皆不逆于鄙见矣。愚陋何必更添蛇足耶。望须由此涵泳。益究昭旷。如何如何。窃详所询诸条。只从文义皮肤上略略爬梳。似无沈潜浓郁以会真腴为亲切受用之意。惟论心处。往往明畅疏朗。然亦只是顺口使气说下。似有欠于循循向此理上做工夫底意思。万乞更将心经近思录二编。逐一下细腻工夫。验之于身。会之于心。一事二事。不容放过。则久久纯熟。自当见此理之非可以粗心大谈而得也。近来龙溪诸公非不凛然于主理之旨。而却暴露声色。见事风生。有处士横议之态。少陋巷如愚之意。犯括囊无咎之戒。区区常用窃叹。今为贤者陈此衷悃。庶企财择。且以达于龙溪公。以质其可否而为之见教也。不任竦企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