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x 页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杂著
杂著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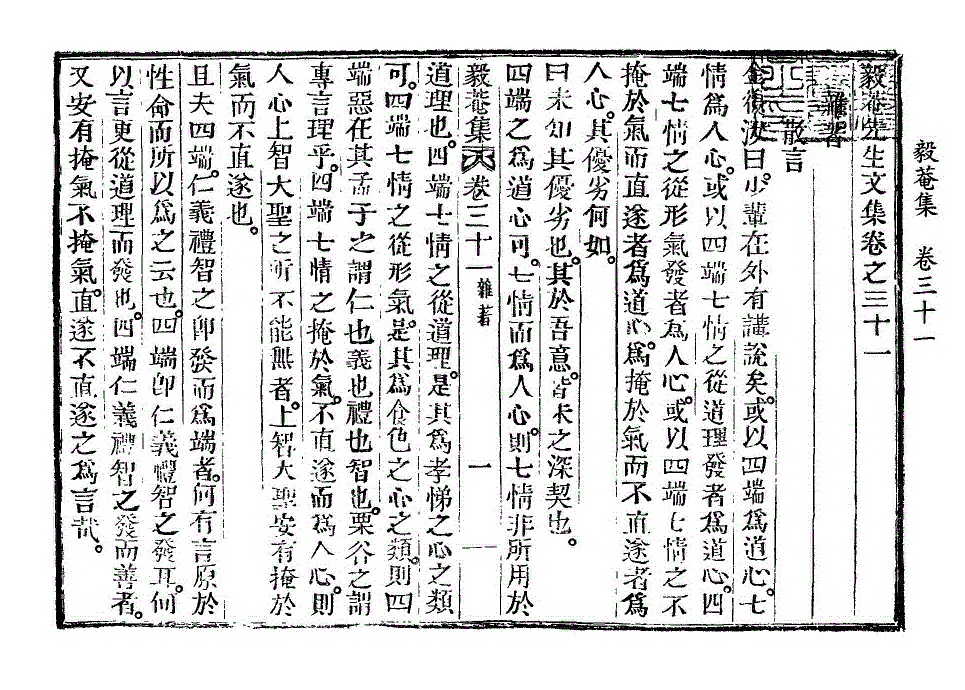 散言
散言金复汝曰。少辈在外有讲说矣。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或以四端七情之从道理发者为道心。四端七情之从形气发者为人心。或以四端七情之不掩于气而直遂者为道心。为掩于气而不直遂者为人心。其优劣何如。
曰未知其优劣也。其于吾意。皆未之深契也。
四端之为道心可。七情而为人心。则七情非所用于道理也。四端七情之从道理。是其为孝悌之心之类可。四端七情之从形气。是其为食色之心之类。则四端恶在其孟子之谓仁也义也礼也智也。栗谷之谓专言理乎。四端七情之掩于气。不直遂而为人心。则人心上智大圣之所不能无者。上智大圣安有掩于气而不直遂也。
且夫四端。仁义礼智之即发而为端者。何有言原于性命而所以为之云也。四端即仁义礼智之发耳。何以言更从道理而发也。四端仁义礼智之发而善者。又安有掩气不掩气。直遂不直遂之为言哉。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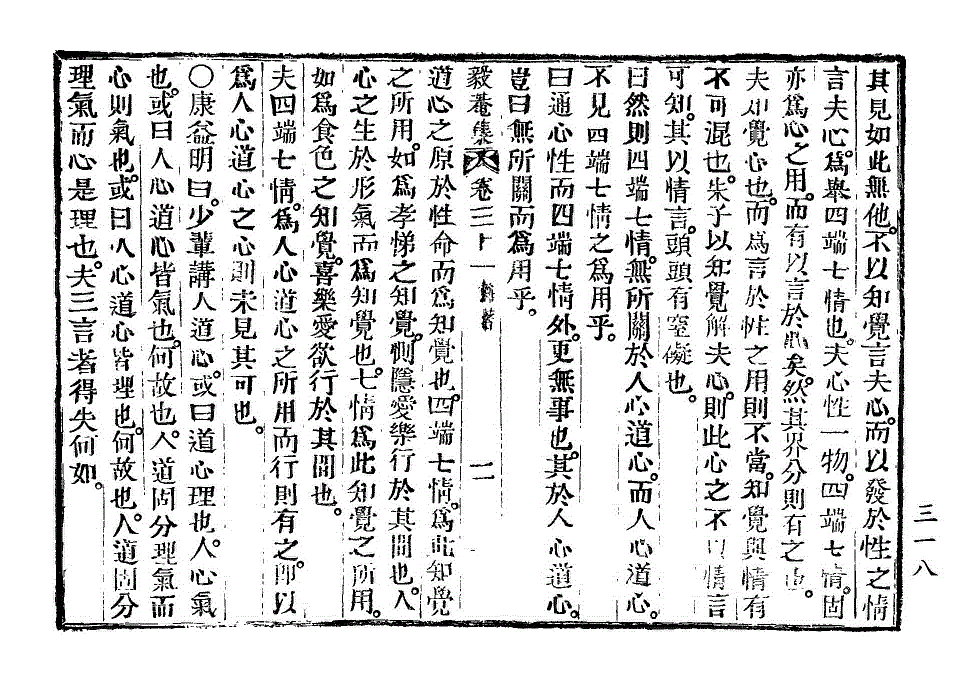 其见如此无他。不以知觉言夫心。而以发于性之情言夫心。为举四端七情也。夫心性一物。四端七情。固亦为心之用。而有以言于心矣。然其界分则有之也。
其见如此无他。不以知觉言夫心。而以发于性之情言夫心。为举四端七情也。夫心性一物。四端七情。固亦为心之用。而有以言于心矣。然其界分则有之也。夫知觉心也。而为言于性之用则不当。知觉与情有不可混也。朱子以知觉解夫心。则此心之不以情言可知。其以情言。头头有窒碍也。
曰然则四端七情。无所关于人心道心。而人心道心。不见四端七情之为用乎。
曰通心性而四端七情外。更无事也。其于人心道心。岂曰无所关而为用乎。
道心之原于性命而为知觉也。四端七情。为此知觉之所用。如为孝悌之知觉。恻隐爱乐行于其间也。人心之生于形气而为知觉也。七情为此知觉之所用。如为食色之知觉。喜乐爱欲行于其间也。
夫四端七情。为人心道心之所用而行则有之。即以为人心道心之心则未见其可也。
○康益明曰。少辈讲人道心。或曰道心理也。人心气也。或曰人心道心皆气也。何故也。人道固分理气而心则气也。或曰人心道心皆理也。何故也。入道固分理气而心是理也。夫三言者得失何如。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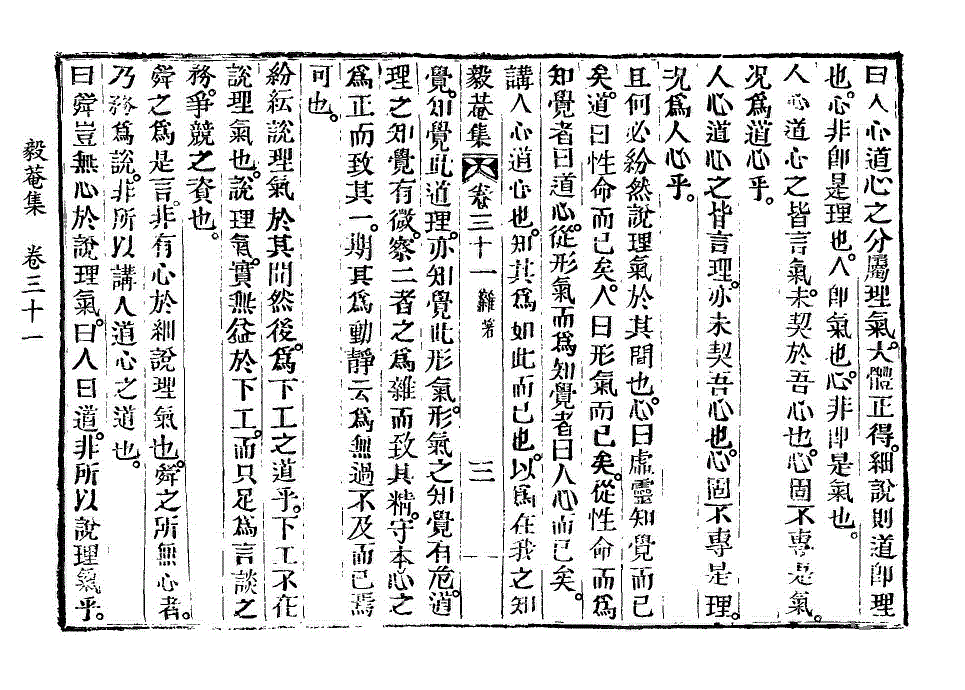 曰人心道心之分属理气。大体正得。细说则道即理也。心非即是理也。人即气也。心非即是气也。
曰人心道心之分属理气。大体正得。细说则道即理也。心非即是理也。人即气也。心非即是气也。人心道心之皆言气。未契于吾心也。心固不专是气。况为道心乎。
人心道心之皆言理。亦未契吾心也。心固不专是理。况为人心乎。
且何必纷然说理气于其间也。心曰虚灵知觉而已矣。道曰性命而已矣。人曰形气而已矣。从性命而为知觉者曰道心。从形气而为知觉者曰人心而已矣。
讲人心道心也。知其为如此而已也。以为在我之知觉。知觉此道理。亦知觉此形气。形气之知觉有危。道理之知觉有微。察二者之为杂而致其精。守本心之为正而致其一。期其为动静云为无过不及而已焉可也。
纷纭说理气于其间然后。为下工之道乎。下工不在说理气也。说理气。实无益于下工。而只足为言谈之务。争竞之资也。
舜之为是言。非有心于细说理气也。舜之所无心者。乃务为说。非所以讲人道心之道也。
曰舜岂无心于说理气。曰人曰道。非所以说理气乎。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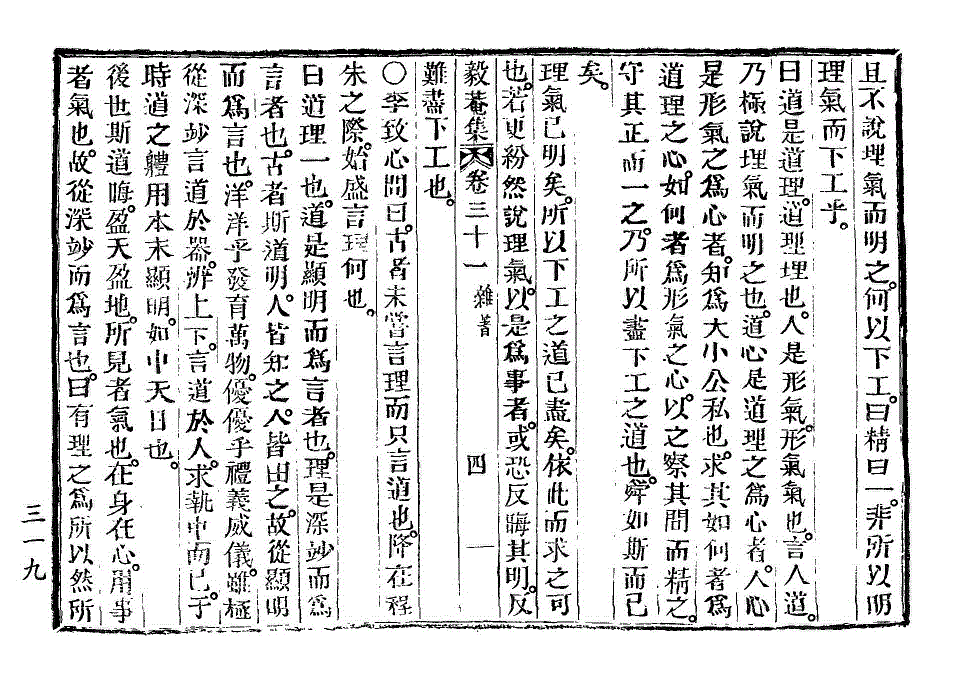 且不说理气而明之。何以下工。曰精曰一。非所以明理气而下工乎。
且不说理气而明之。何以下工。曰精曰一。非所以明理气而下工乎。曰道是道理。道理理也。人是形气。形气气也。言人道。乃极说理气而明之也。道心是道理之为心者。人心是形气之为心者。知为大小公私也。求其如何者为道理之心。如何者为形气之心。以之察其间而精之。守其正而一之。乃所以尽下工之道也。舜如斯而已矣。
理气已明矣。所以下工之道已尽矣。依此而求之可也。若更纷然说理气。以是为事者。或恐反晦其明。反难尽下工也。
○李致心问曰。古者未尝言理而只言道也。降在程朱之际。始盛言理何也。
曰道理一也。道是显明而为言者也。理是深妙而为言者也。古者斯道明。人皆知之。人皆由之。故从显明而为言也。洋洋乎发育万物。优优乎礼义威仪。虽极从深妙言道于器。辨上下。言道于人。求执中而已。于时道之体用本末显明。如中天日也。
后世斯道晦。盈天盈地。所见者气也。在身在心。用事者气也。故从深妙而为言也。曰有理之为所以然所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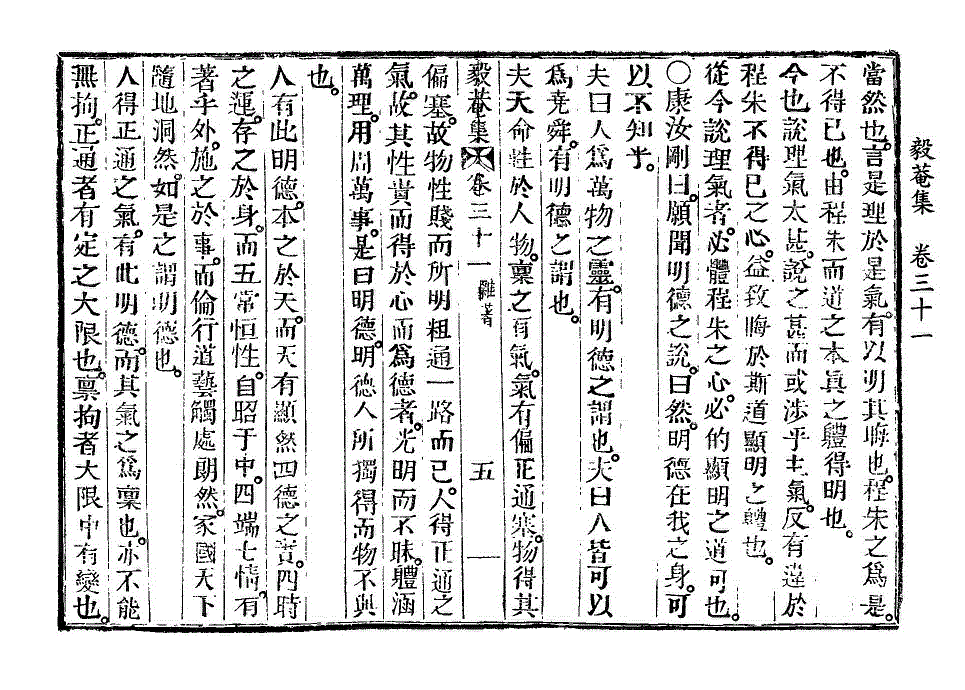 当然也。言是理于是气。有以明其晦也。程朱之为是。不得已也。由程朱而道之本真之体得明也。
当然也。言是理于是气。有以明其晦也。程朱之为是。不得已也。由程朱而道之本真之体得明也。今也说理气太甚。说之甚而或涉乎主气。反有违于程朱不得已之心。益致晦于斯道显明之体也。
从今说理气者。必体程朱之心。必的显明之道可也。
○康汝刚曰。愿闻明德之说。曰然。明德在我之身。可以不知乎。
夫曰人为万物之灵。有明德之谓也。夫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明德之谓也。
夫天命性于人物。禀之有气。气有偏正通塞。物得其偏塞。故物性贱而所明粗通一路而已。人得正通之气。故其性贵而得于心而为德者。光明而不昧。体涵万理。用周万事。是曰明德。明德人所独得而物不与也。
人有此明德。本之于天。而天有显然四德之实。四时之运。存之于身。而五常恒性。自昭于中。四端七情。有著乎外。施之于事。而伦行道艺触处朗然。家国天下随地洞然。如是之谓明德也。
人得正通之气。有此明德。而其气之为禀也。亦不能无拘。正通者有定之大限也。禀拘者大限中有变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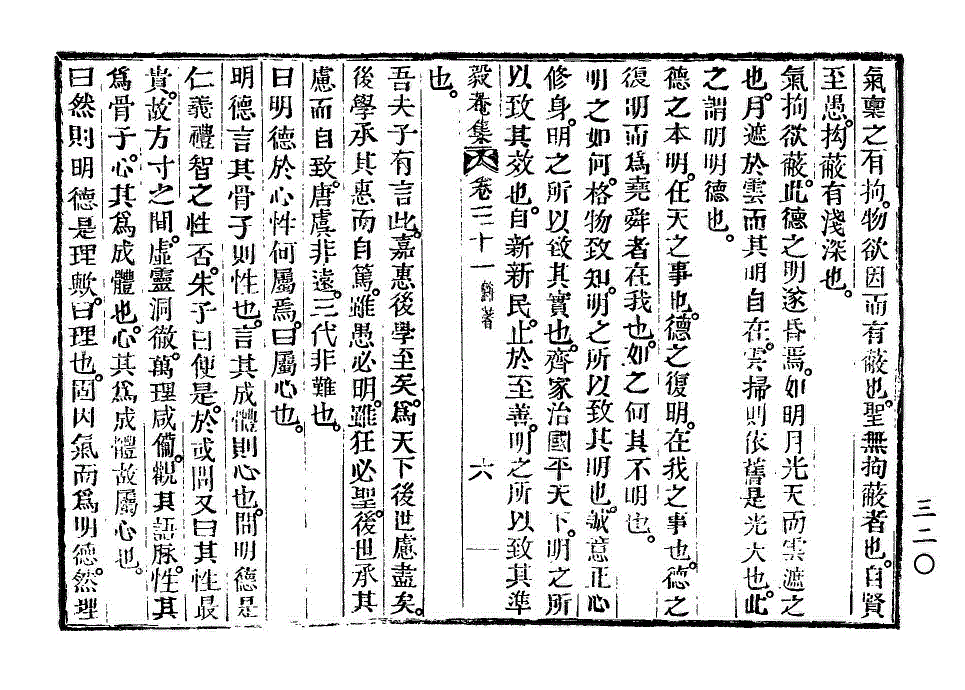 气禀之有拘。物欲因而有蔽也。圣无拘蔽者也。自贤至愚。拘蔽有浅深也。
气禀之有拘。物欲因而有蔽也。圣无拘蔽者也。自贤至愚。拘蔽有浅深也。气拘欲蔽。此德之明遂昏焉。如明月光天而云遮之也。月遮于云而其明自在。云扫则依旧是光大也。此之谓明明德也。
德之本明。在天之事也。德之复明。在我之事也。德之复明而为尧舜者在我也。如之何其不明也。
明之如何。格物致知。明之所以致其明也。诚意正心修身。明之所以致其实也。齐家治国平天下。明之所以致其效也。自新新民。止于至善。明之所以致其准也。
吾夫子有言此。嘉惠后学至矣。为天下后世虑尽矣。后学承其惠而自笃。虽愚必明。虽狂必圣。后世承其虑而自致。唐虞非远。三代非难也。
曰明德于心性何属焉。曰属心也。
明德言其骨子则性也。言其成体则心也。间明德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朱子曰便是。于或问又曰其性最贵。故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观其语脉。性其为骨子。心其为成体也。心其为成体故属心也。
曰然则明德是理欤。曰理也。固因气而为明德。然理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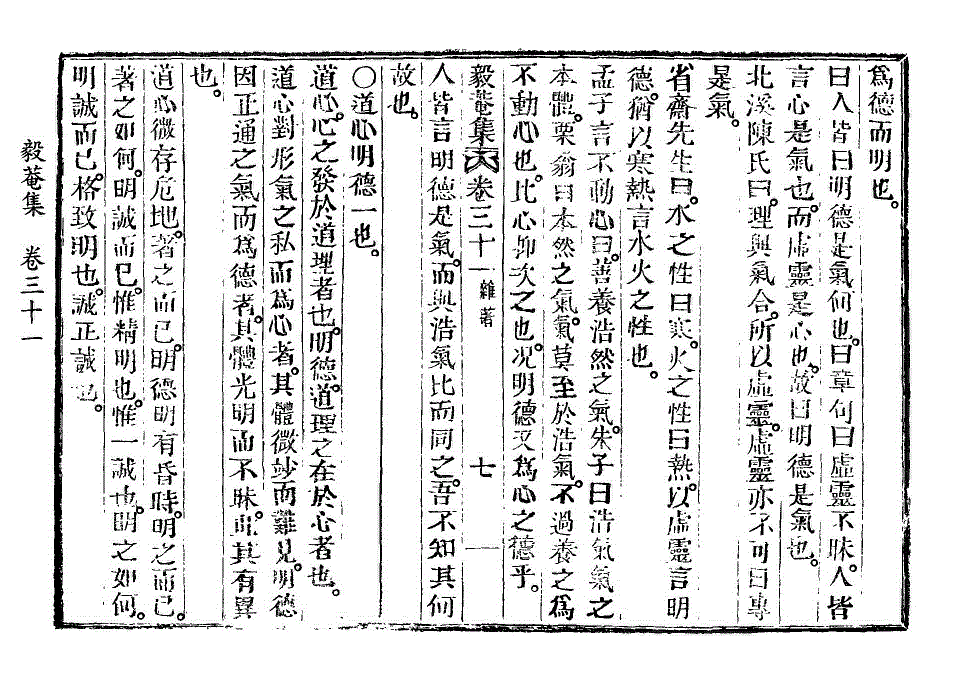 为德而明也。
为德而明也。曰人皆曰明德是气何也。曰章句曰虚灵不昧。人皆言心是气也。而虚灵是心也。故曰明德是气也。
北溪陈氏曰。理与气合。所以虚灵。虚灵亦不可曰专是气。
省斋先生曰。水之性曰寒。火之性曰热。以虚灵言明德。犹以寒热言水火之性也。
孟子言不动心曰。善养浩然之气。朱子曰浩气气之本体。栗翁曰本然之气。气莫至于浩气。不过养之为不动心也。比心抑次之也。况明德又为心之德乎。
人皆言明德是气。而与浩气比而同之。吾不知其何故也。
○道心明德一也。
道心。心之发于道理者也。明德。道理之在于心者也。
道心对形气之私而为心者。其体微妙而难见。明德因正通之气而为德者。其体光明而不昧。此其有异也。
道心微存危地。著之而已。明德明有昏时。明之而已。著之如何。明诚而已。惟精明也。惟一诚也。明之如何。明诚而已。格致明也。诚正诚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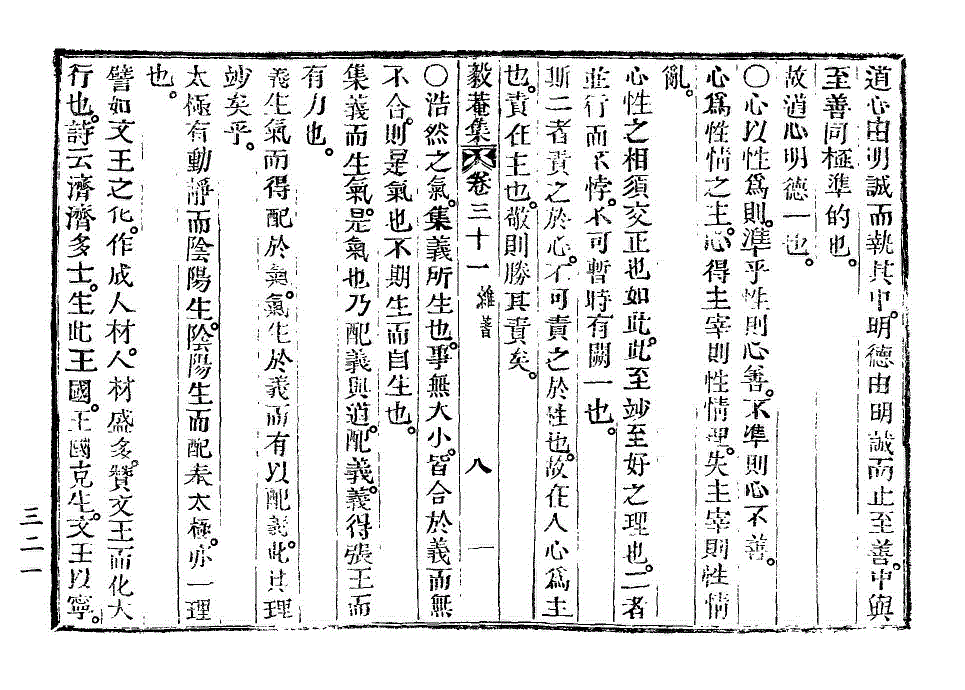 道心由明诚而执其中。明德由明诚而止至善。中与至善同极准的也。
道心由明诚而执其中。明德由明诚而止至善。中与至善同极准的也。故道心明德一也。
○心以性为则。准乎性则心善。不准则心不善。
心为性情之主。心得主宰则性情理。失主宰则性情乱。
心性之相须交正也如此。此至妙至好之理也。二者并行而不悖。不可暂时有阙一也。
斯二者责之于心。不可责之于性也。故在人心为主也。责在主也。敬则胜其责矣。
○浩然之气。集义所生也。事无大小。皆合于义而无不合。则是气也不期生而自生也。
集义而生气。是气也乃配义与道。配义。义得张王而有力也。
义生气而得配于气。气生于义而有以配义。此其理妙矣乎。
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生而配奉太极。亦一理也。
譬如文王之化。作成人材。人材盛多。赞文王而化大行也。诗云济济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文王以宁。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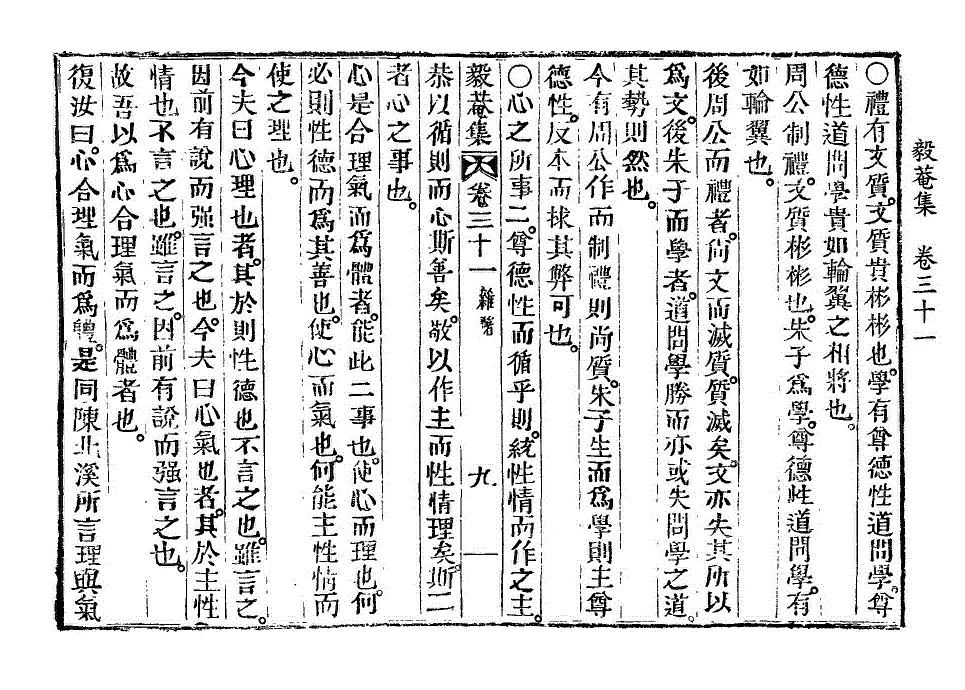 ○礼有文质。文质贵彬彬也。学有尊德性道问学。尊德性道问学贵如轮翼之相将也。
○礼有文质。文质贵彬彬也。学有尊德性道问学。尊德性道问学贵如轮翼之相将也。周公制礼。文质彬彬也。朱子为学。尊德性道问学。有如轮翼也。
后周公而礼者。尚文而灭质。质灭矣。文亦失其所以为文。后朱子而学者。道问学胜而亦或失问学之道。其势则然也。
今有周公作而制礼则尚质。朱子生而为学则主尊德性。反本而救其弊可也。
○心之所事二。尊德性而循乎则。统性情而作之主。恭以循则而心斯善矣。敬以作主而性情理矣。斯二者心之事也。
心是合理气而为体者。能此二事也。使心而理也。何必则性德而为其善也。使心而气也。何能主性情而使之理也。
今夫曰心理也者。其于则性德也不言之也。虽言之。因前有说而强言之也。今夫曰心气也者。其于主性情也不言之也。虽言之。因前有说而强言之也。
故吾以为心合理气而为体者也。
复汝曰。心合理气而为体。是同陈北溪所言理与气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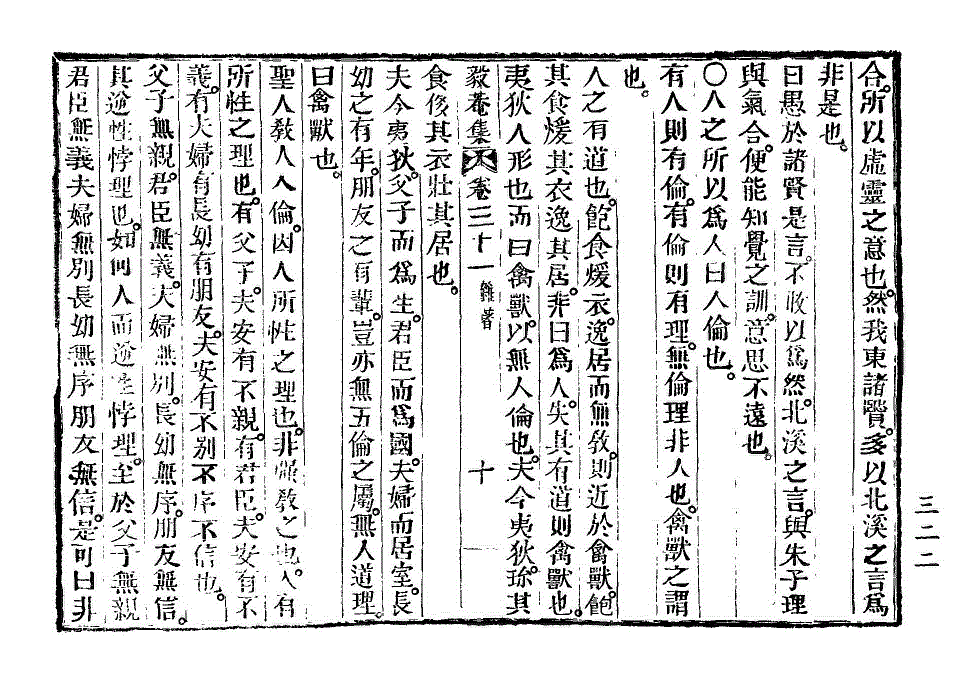 合。所以虚灵之意也。然我东诸贤。多以北溪之言为非是也。
合。所以虚灵之意也。然我东诸贤。多以北溪之言为非是也。曰愚于诸贤是言。不敢以为然。北溪之言。与朱子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之训。意思不远也。
○人之所以为人曰人伦也。
有人则有伦。有伦则有理。无伦理非人也。禽兽之谓也。
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饱其食煖其衣逸其居。非曰为人。失其有道则禽兽也。夷狄人形也而曰禽兽。以无人伦也。夫今夷狄。珍其食侈其衣壮其居也。
夫今夷狄。父子而为生。君臣而为国。夫妇而居室。长幼之有年。朋友之有辈。岂亦无五伦之属。无人道理。曰禽兽也。
圣人教人人伦。因人所性之理也。非强教之也。人有所性之理也。有父子。夫安有不亲。有君臣。夫安有不义。有夫妇有长幼有朋友。夫安有不别不序不信也。
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夫妇无别。长幼无序。朋友无信。其逆性悖理也。如何人而逆性悖理。至于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夫妇无别长幼无序朋友无信。是可曰非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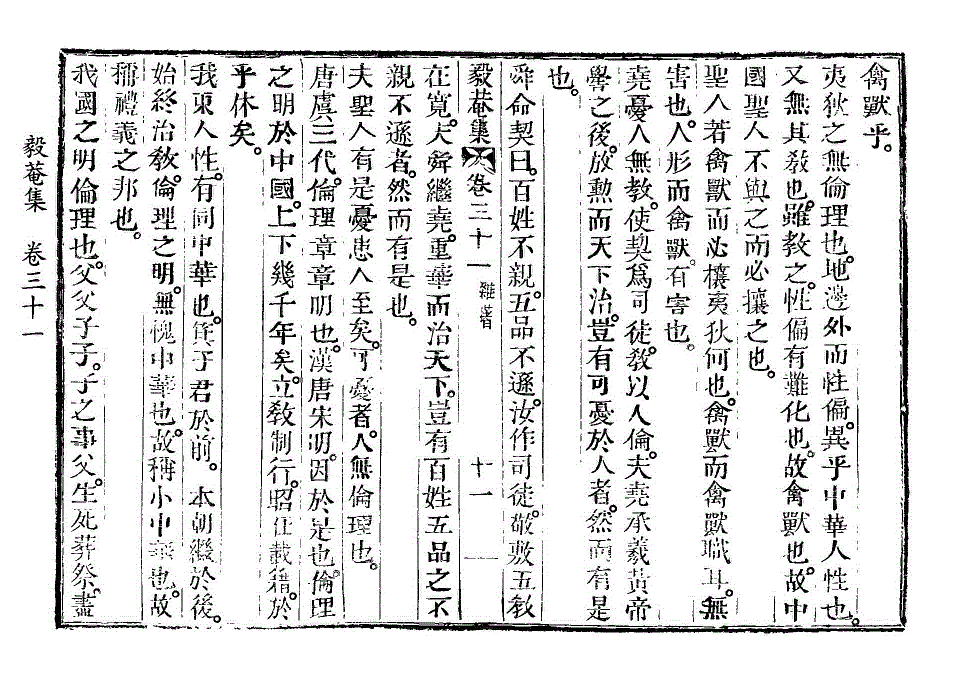 禽兽乎。
禽兽乎。夷狄之无伦理也。地边外而性偏。异乎中华人性也。又无其教也。虽教之。性偏有难化也。故禽兽也。故中国圣人不与之而必攘之也。
圣人若禽兽而必攘夷狄何也。禽兽而禽兽职耳。无害也。人形而禽兽。有害也。
尧忧人无教。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夫尧承羲黄帝喾之后。放勋而天下治。岂有可忧于人者。然而有是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夫舜继尧。重华而治天下。岂有百姓五品之不亲不逊者。然而有是也。
夫圣人有是忧患人至矣。可忧者。人无伦理也。
唐虞三代。伦理章章明也。汉唐宋明。因于是也。伦理之明于中国。上下几千年矣。立教制行。昭在载籍。于乎休矣。
我东人性。有同中华也。箕子君于前。 本朝继于后。始终治教。伦理之明。无愧中华也。故称小中华也。故称礼义之邦也。
我国之明伦理也。父父子子。子之事父。生死葬祭。尽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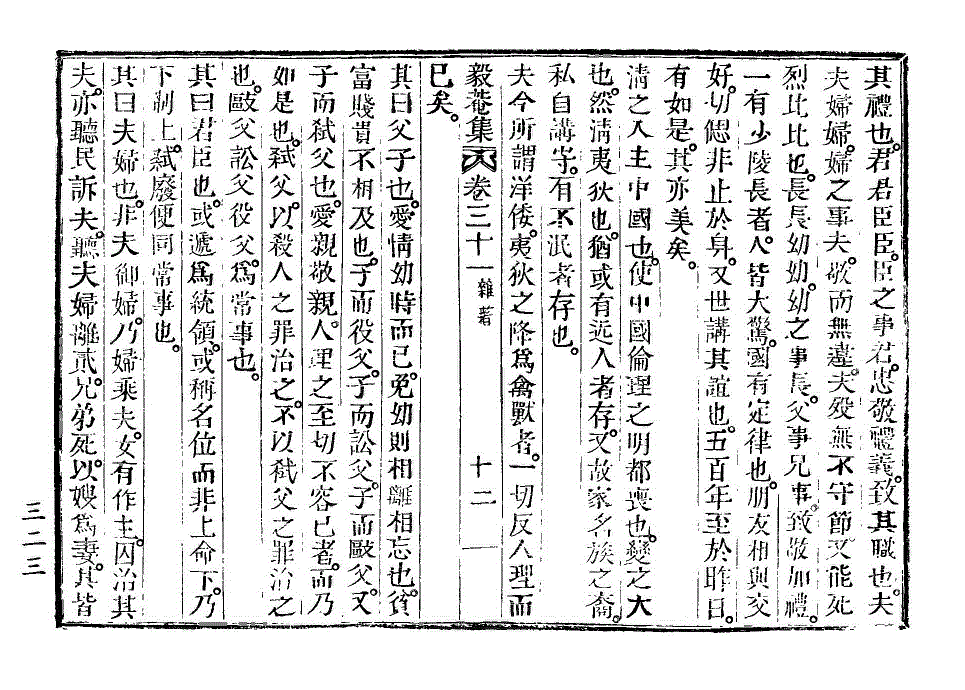 其礼也。君君臣臣。臣之事君。忠敬礼义。致其职也。夫夫妇妇。妇之事夫。敬而无违。夫殁无不守节。又能死烈比比也。长长幼幼。幼之事长。父事兄事。致敬加礼。一有少陵长者。人皆大惊。国有定律也。朋友相与交好。切偲非止于身。又世讲其谊也。五百年至于昨日。有如是。其亦美矣。
其礼也。君君臣臣。臣之事君。忠敬礼义。致其职也。夫夫妇妇。妇之事夫。敬而无违。夫殁无不守节。又能死烈比比也。长长幼幼。幼之事长。父事兄事。致敬加礼。一有少陵长者。人皆大惊。国有定律也。朋友相与交好。切偲非止于身。又世讲其谊也。五百年至于昨日。有如是。其亦美矣。清之入主中国也。使中国伦理之明都丧也。变之大也。然清夷狄也。犹或有近人者存。又故家名族之裔。私自讲守。有不泯者存也。
夫今所谓洋倭。夷狄之降为禽兽者。一切反人理而已矣。
其曰父子也。爱情幼时而已。免幼则相离相忘也。贫富贱贵不相及也。子而役父。子而讼父。子而驱父。又子而弑父也。爱亲敬亲。人理之至切不容已者。而乃如是也。弑父。以杀人之罪治之。不以弑父之罪治之也。驱父讼父役父。为常事也。
其曰君臣也。或递为统领。或称名位而非上命下。乃下制上。弑废便同常事也。
其曰夫妇也。非夫御妇。乃妇乘夫。女有作主。囚治其夫。亦听民诉夫。听夫妇离贰。兄弟死。以嫂为妻。其皆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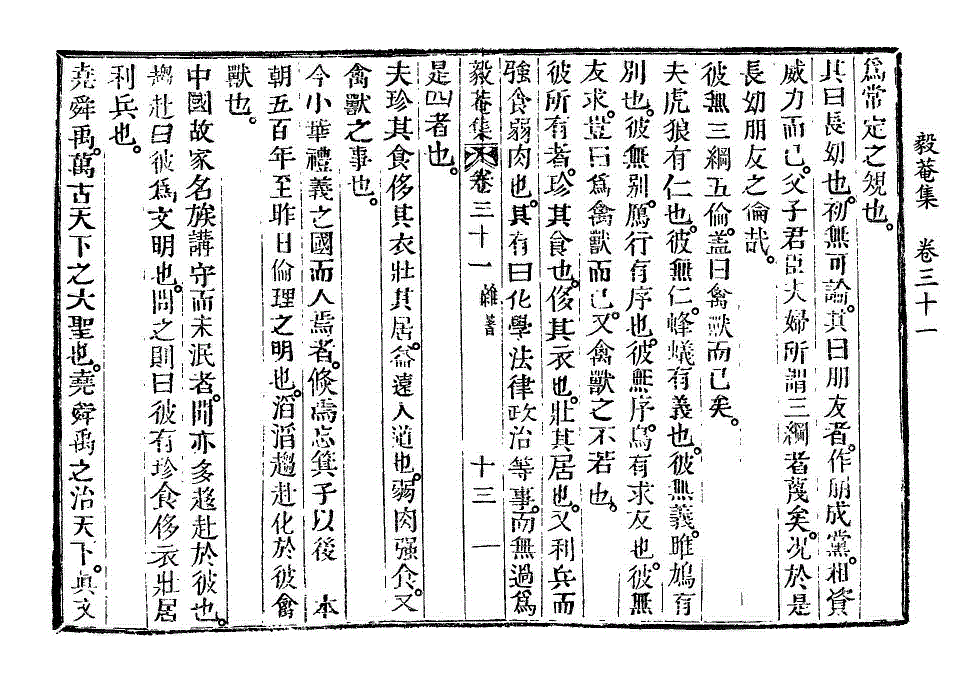 为常定之规也。
为常定之规也。其曰长幼也。初无可论。其曰朋友者。作朋成党。相资威力而已。父子君臣夫妇所谓三纲者蔑矣。况于是长幼朋友之伦哉。
彼无三纲五伦。盖曰禽兽而已矣。
夫虎狼有仁也。彼无仁。蜂蚁有义也。彼无义。雎鸠有别也。彼无别。雁行有序也。彼无序。鸟有求友也。彼无友求。岂曰为禽兽而已。又禽兽之不若也。
彼所有者。珍其食也。侈其衣也。壮其居也。又利兵而强食弱肉也。其有曰化学法律政治等事。而无过为是四者也。
夫珍其食侈其衣壮其居。益远人道也。弱肉强食。又禽兽之事也。
今小华礼义之国而人焉者。倏焉忘箕子以后 本朝五百年至昨日伦理之明也。滔滔趋赴化于彼禽兽也。
中国故家名族讲守而未泯者。闻亦多趍赴于彼也。趋赴曰彼为文明也。问之则曰彼有珍食侈衣壮居利兵也。
尧舜禹。万古天下之大圣也。尧舜禹之治天下。真文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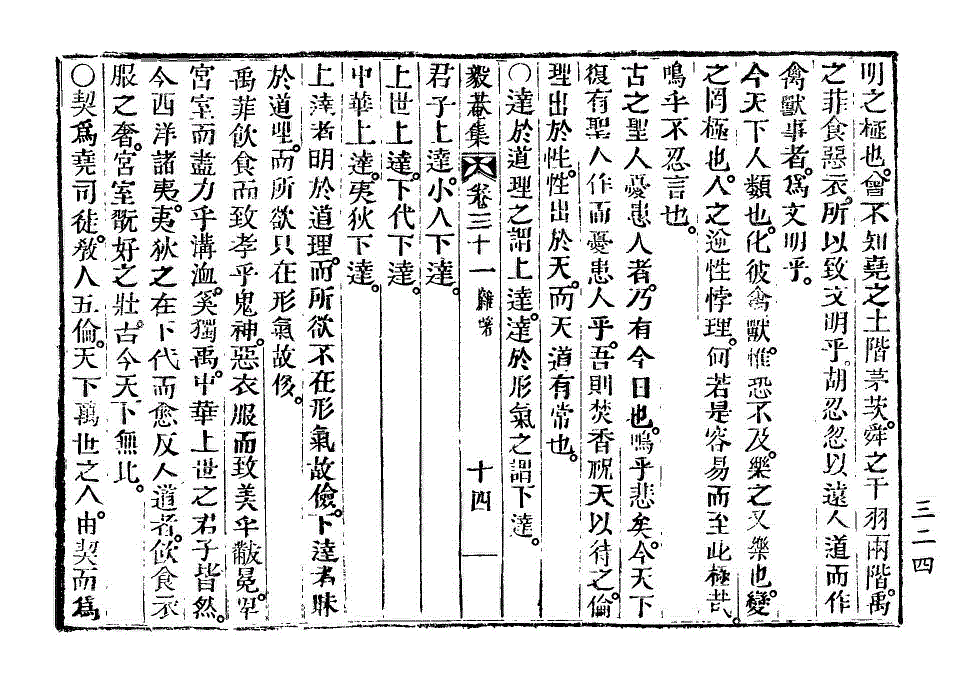 明之极也。曾不知尧之土阶茅茨。舜之干羽两阶。禹之菲食恶衣。所以致文明乎。胡忍忽以远人道而作禽兽事者。为文明乎。
明之极也。曾不知尧之土阶茅茨。舜之干羽两阶。禹之菲食恶衣。所以致文明乎。胡忍忽以远人道而作禽兽事者。为文明乎。今天下人类也。化彼禽兽。惟恐不及。乐之又乐也。变之罔极也。人之逆性悖理。何若是容易而至此极哉。呜乎不忍言也。
古之圣人忧患人者。乃有今日也。呜乎悲矣。今天下复有圣人作而忧患人乎。吾则焚香祝天以待之。伦理出于性。性出于天。而天道有常也。
○达于道理之谓上达。达于形气之谓下达。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上世上达。下代下达。
中华上达。夷狄下达。
上达者明于道理。而所欲不在形气故俭。下达者昧于道理。而所欲只在形气故侈。
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奚独禹。中华上世之君子皆然。今西洋诸夷。夷狄之在下代而愈反人道者。饮食衣服之奢。宫室玩好之壮。古今天下无比。
○契为尧司徒。教人五伦。天下万世之人。由契而为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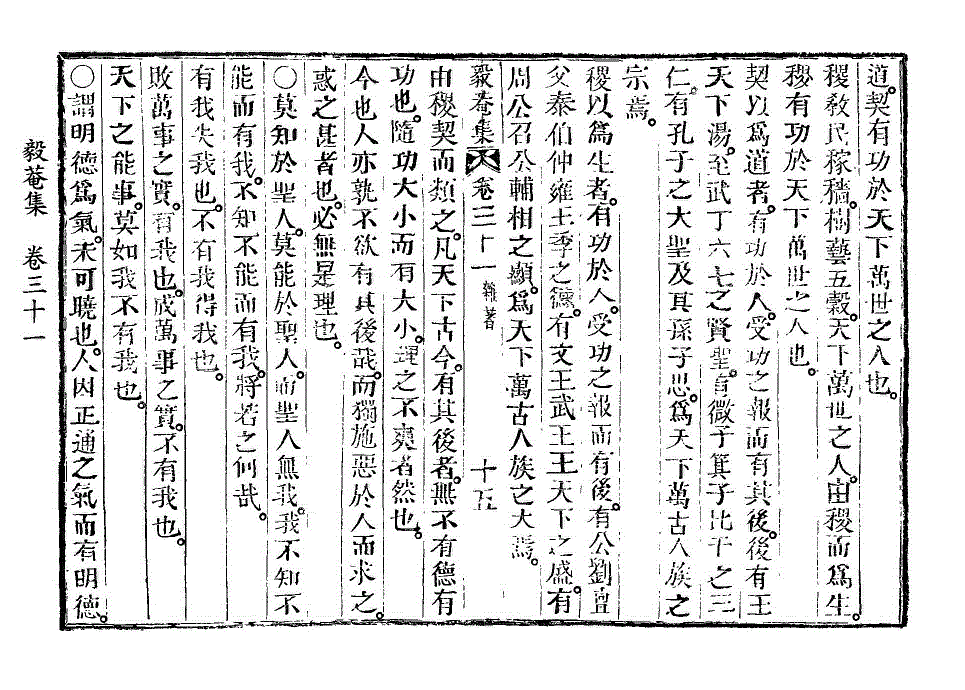 道。契有功于天下万世之人也。
道。契有功于天下万世之人也。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天下万世之人。由稷而为生。稷有功于天下万世之人也。
契以为道者。有功于人。受功之报而有其后。后有王天下汤。至武丁六七之贤圣。有微子箕子比干之三仁。有孔子之大圣及其孙子思。为天下万古人族之宗焉。
稷以为生者。有功于人。受功之报而有后。有公刘亶父泰伯仲雍王季之德。有文王武王王天下之盛。有周公召公辅相之显。为天下万古人族之大焉。
由稷契而类之。凡天下古今。有其后者。无不有德有功也。随功大小而有大小。理之不爽者然也。
今也人亦孰不欲有其后哉。而独施恶于人而求之。惑之甚者也。必无是理也。
○莫知于圣人。莫能于圣人。而圣人无我。我不知不能而有我。不知不能而有我。将若之何哉。
有我失我也。不有我得我也。
败万事之实。有我也。成万事之实。不有我也。
天下之能事。莫如我不有我也。
○谓明德为气。未可晓也。人因正通之气而有明德。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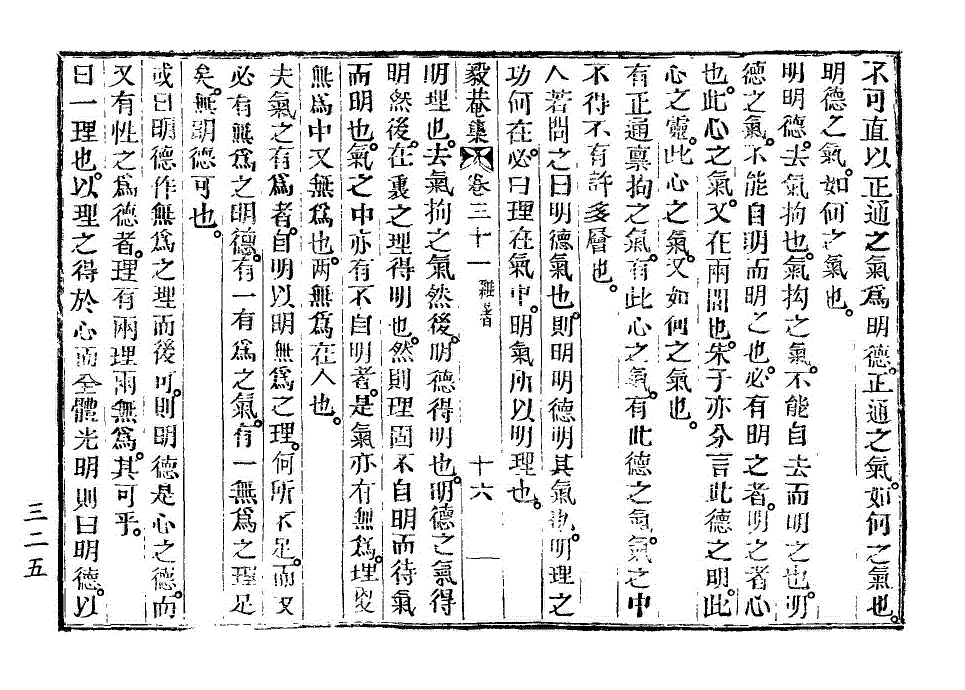 不可直以正通之气为明德。正通之气。如何之气也。明德之气。如何之气也。
不可直以正通之气为明德。正通之气。如何之气也。明德之气。如何之气也。明明德。去气拘也。气拘之气。不能自去而明之也。明德之气。不能自明而明之也。必有明之者。明之者心也。此心之气。又在两间也。朱子亦分言此德之明。此心之灵。此心之气。又如何之气也。
有正通禀拘之气。有此心之气。有此德之气。气之中不得不有许多层也。
人若问之曰明德气也。则明明德明其气也。明理之功何在。必曰理在气中。明气所以明理也。
明理也。去气拘之气然后。明德得明也。明德之气得明然后。在里之理得明也。然则理固不自明而待气而明也。气之中亦有不自明者。是气亦有无为。理更无为中又无为也。两无为在人也。
夫气之有为者。自明以明无为之理。何所不足。而又必有无为之明德。有一有为之气。有一无为之理足矣。无明德可也。
或曰明德作无为之理而后可。则明德是心之德。而又有性之为德者。理有两理两无为。其可乎。
曰一理也。以理之得于心而全体光明则曰明德。以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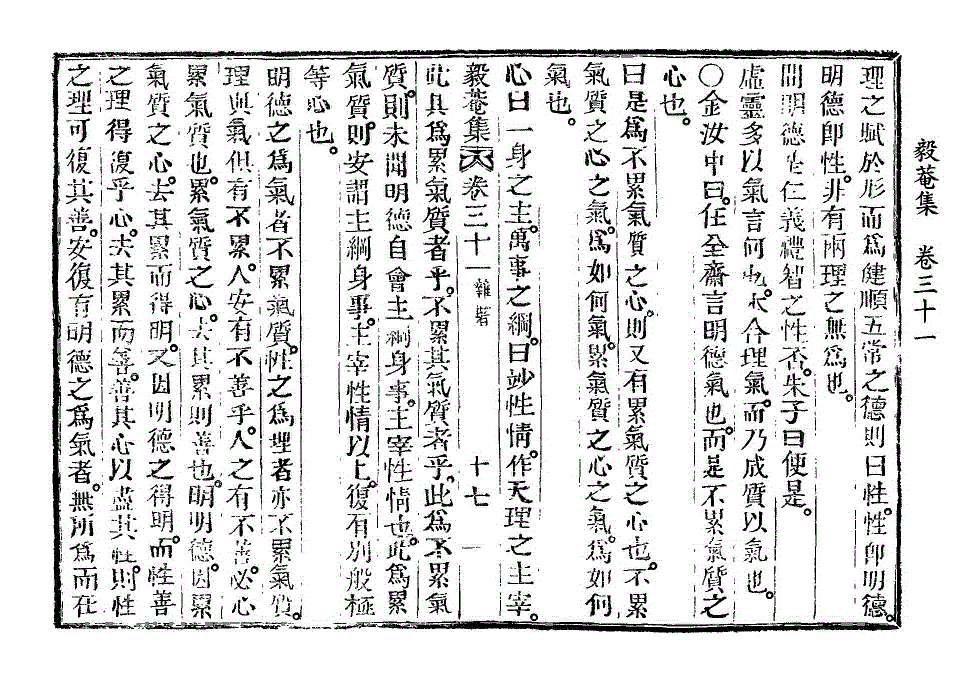 理之赋于形而为健顺五常之德则曰性。性即明德。明德即性。非有两理之无为也。
理之赋于形而为健顺五常之德则曰性。性即明德。明德即性。非有两理之无为也。间明德是仁义礼智之性否。朱子曰便是。
虚灵多以气言何也。本合理气。而乃成质以气也。
○金汝中曰。任全斋言明德气也。而是不累气质之心也。
曰是为不累气质之心。则又有累气质之心也。不累气质之心之气。为如何气。累气质之心之气。为如何气也。
心曰一身之主。万事之纲。曰妙性情。作天理之主宰。此具为累气质者乎。不累其气质者乎。此为不累气质。则未闻明德自会主纲身事。主宰性情也。此为累气质。则安谓主纲身事。主宰性情以上。复有别般极等心也。
明德之为气者不累气质。性之为理者亦不累气质。理与气俱有不累。人安有不善乎。人之有不善。必心累气质也。累气质之心。去其累则善也。明明德。因累气质之心。去其累而得明。又因明德之得明。而性善之理得复乎心。去其累而善。善其心以尽其性。则性之理可复其善。安复有明德之为气者。无所为而在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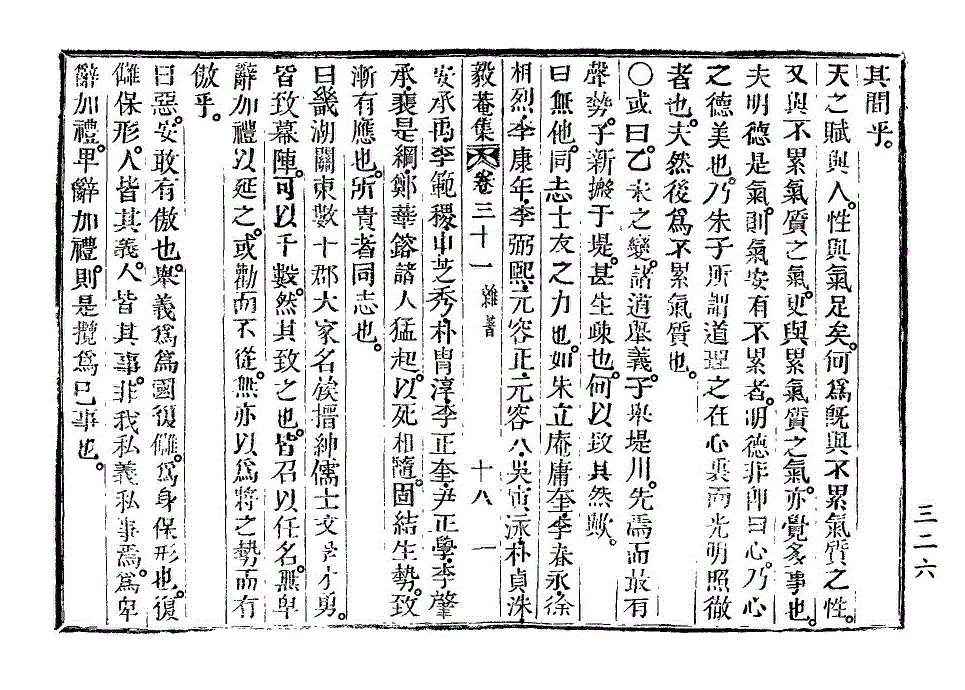 其间乎。
其间乎。天之赋与人。性与气足矣。何为既与不累气质之性。又与不累气质之气。更与累气质之气。亦觉多事也。夫明德是气。则气安有不累者。明德非即曰心。乃心之德美也。乃朱子所谓道理之在心里而光明照彻者也。夫然后为不累气质也。
○或曰。乙未之变。诸道举义。子举堤川。先焉而最有声势。子新搬于堤。甚生疏也。何以致其然欤。
曰无他。同志士友之力也。如朱立庵庸奎,李春永,徐相烈,李康年,李弼熙,元容正,元容八,吴寅泳,朴贞洙,安承禹,李范稷,申芝秀,朴胄淳,李正奎,尹正学,李肇承,裴是纲,郑华镕诸人猛起。以死相随。固结生势。致渐有应也。所贵者同志也。
曰畿湖关东数十郡大家名族搢绅儒士文学才勇。皆致幕阵。可以千数。然其致之也。皆召以任名。无卑辞加礼以延之。或劝而不从。无亦以为将之势而有傲乎。
曰恶。安敢有傲也。举义为为国复雠。为身保形也。复雠保形。人皆其义。人皆其事。非我私义私事焉。为卑辞加礼。卑辞加礼。则是揽为己事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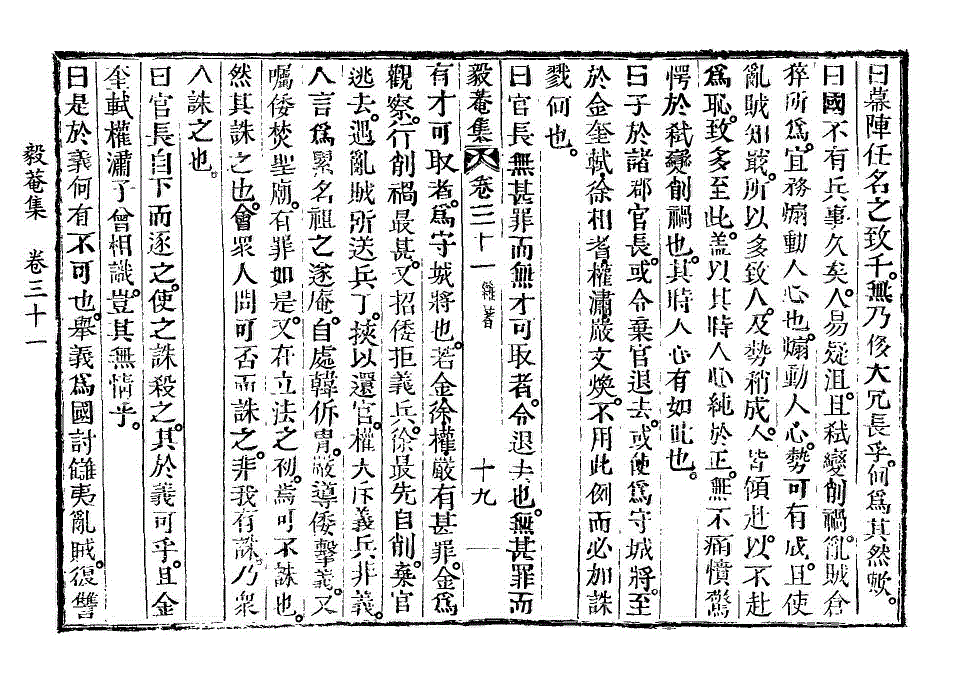 曰幕阵任名之致千。无乃侈大冗长乎。何为其然欤。
曰幕阵任名之致千。无乃侈大冗长乎。何为其然欤。曰国不有兵事久矣。人易疑沮。且弑变削祸。乱贼仓猝所为。宜务煽动人心也。煽动人心。势可有成。且使乱贼知戢。所以多致人。及势稍成。人皆倾赴。以不赴为耻。致多至此。盖以其时人心纯于正。无不痛愤惊愕于弑变削祸也。其时人心有如此也。
曰子于诸郡官长。或令弃官退去。或使为守城将。至于金奎轼,徐相耆,权潚,严文焕。不用此例而必加诛戮何也。
曰官长无甚罪而无才可取者。令退去也。无甚罪而有才可取者。为守城将也。若金,徐,权,严有甚罪。金为观察。行削祸最甚。又招倭拒义兵。徐最先自削。弃官逃去。遇乱贼所送兵丁。挟以还官。权大斥义兵非义。人言为累名祖之遂庵。自处韩𠈁胄。严导倭击义。又嘱倭焚圣庙。有罪如是。又在立法之初。焉可不诛也。然其诛之也。会众人问可否而诛之。非我有诛。乃众人诛之也。
曰官长自下而逐之。使之诛杀之。其于义可乎。且金奎轼权潚子曾相识。岂其无情乎。
曰是于义何有不可也。举义为国讨雠夷乱贼。复雠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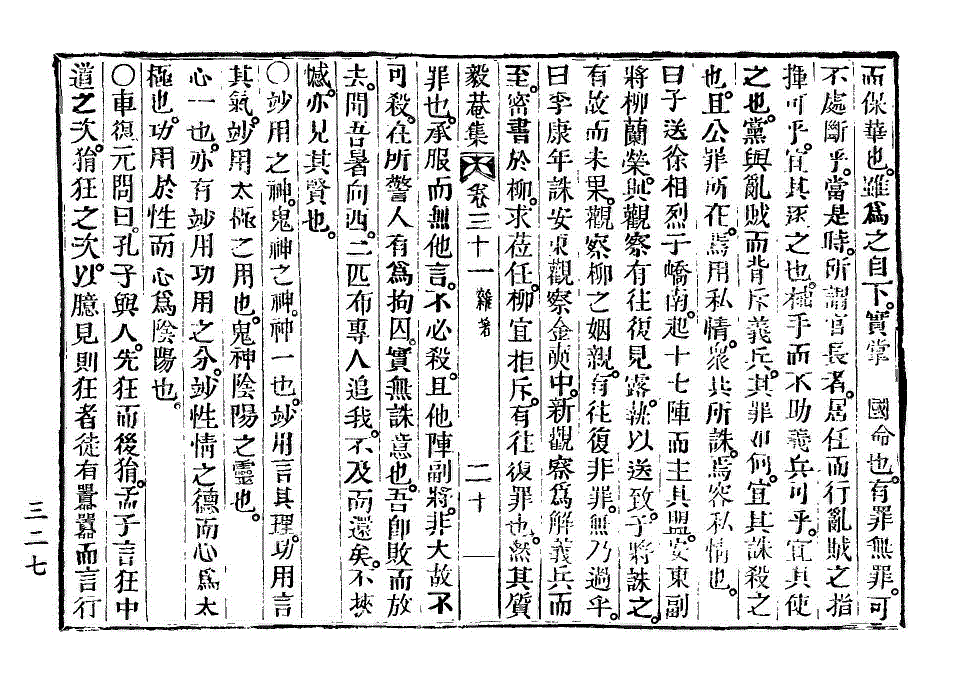 而保华也。虽为之自下。实掌 国命也。有罪无罪。可不处断乎。当是时。所谓官长者。居任而行乱贼之指挥可乎。宜其逐之也。袖手而不助义兵可乎。宜其使之也。党与乱贼而背斥义兵。其罪如何。宜其诛杀之也。且公罪所在。焉用私情。众共所诛。焉容私情也。
而保华也。虽为之自下。实掌 国命也。有罪无罪。可不处断乎。当是时。所谓官长者。居任而行乱贼之指挥可乎。宜其逐之也。袖手而不助义兵可乎。宜其使之也。党与乱贼而背斥义兵。其罪如何。宜其诛杀之也。且公罪所在。焉用私情。众共所诛。焉容私情也。曰子送徐相烈子峤南。起十七阵而主其盟。安东副将柳兰荣。与观察有往复见露。执以送致。子将诛之。有故而未果。观察柳之姻亲。有往复非罪。无乃过乎。曰李康年诛安东观察金奭中。新观察为解义兵而至。密书于柳。求莅任。柳宜拒斥。有往复罪也。然其质罪也。承服而无他言。不必杀。且他阵副将。非大故不可杀。在所警人有为拘囚。实无诛意也。吾即败而放去。闻吾暑向西。二匹布专人追我。不及而还矣。不挟憾。亦见其贤也。
○妙用之神。鬼神之神。神一也。妙用言其理。功用言其气。妙用太极之用也。鬼神阴阳之灵也。
心一也。亦有妙用功用之分。妙性情之德而心为太极也。功用于性而心为阴阳也。
○车复元问曰。孔子与人。先狂而后狷。孟子言狂中道之次。狷狂之次。以臆见则狂者徒有嚣嚣而言行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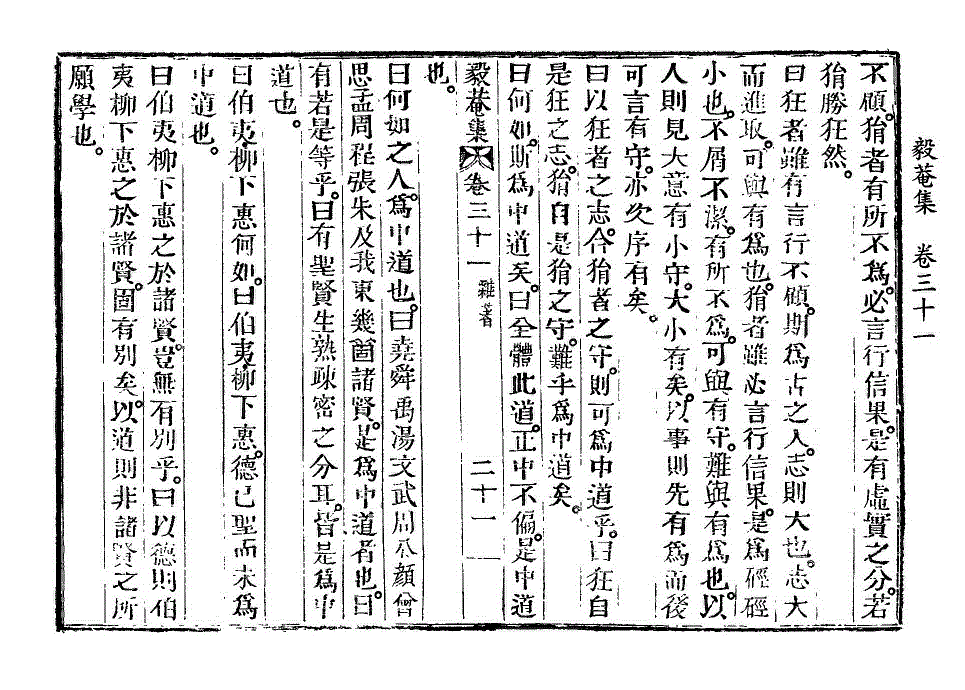 不顾。狷者有所不为。必言行信果。是有虚实之分。若狷胜狂然。
不顾。狷者有所不为。必言行信果。是有虚实之分。若狷胜狂然。曰狂者虽有言行不顾。期为古之人。志则大也。志大而进取。可与有为也。狷者虽必言行信果。是为硁硁小也。不屑不洁。有所不为。可与有守。难与有为也。以人则见大意有小守。大小有矣。以事则先有为而后可言有守。亦次序有矣。
曰以狂者之志。合狷者之守。则可为中道乎。曰狂自是狂之志。狷自是狷之守。难乎为中道矣。
曰何如。斯为中道矣。曰全体此道。正中不偏。是中道也。
曰何如之人。为中道也。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颜曾思孟周程张朱及我东几个诸贤。是为中道者也。曰有若是等乎。曰有圣贤生熟疏密之分耳。皆是为中道也。
曰伯夷,柳下惠何如。曰伯夷,柳下惠。德已圣而未为中道也。
曰伯夷,柳下惠之于诸贤。岂无有别乎。曰以德则伯夷,柳下惠之于诸贤。固有别矣。以道则非诸贤之所愿学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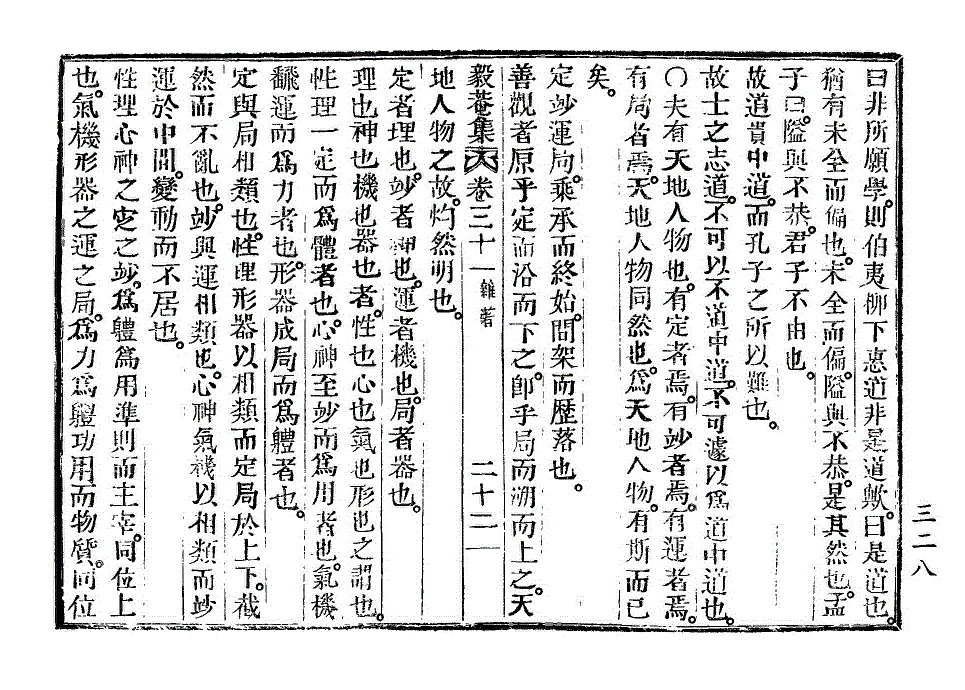 曰非所愿学。则伯夷,柳下惠道非是道欤。曰是道也。犹有未全而偏也。未全而偏。隘与不恭。是其然也。孟子曰。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曰非所愿学。则伯夷,柳下惠道非是道欤。曰是道也。犹有未全而偏也。未全而偏。隘与不恭。是其然也。孟子曰。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故道贵中道。而孔子之所以难也。
故士之志道。不可以不道中道。不可遽以为道中道也。
○夫有天地人物也。有定者焉。有妙者焉。有运者焉。有局者焉。天地人物同然也。为天地人物。有斯而已矣。
定妙运局。乘承而终始。问架而历落也。
善观者原乎定而沿而下之。即乎局而溯而上之。天地人物之故。灼然明也。
定者理也。妙者神也。运者机也。局者器也。
理也神也机也器也者。性也心也气也形也之谓也。性理一定而为体者也。心神至妙而为用者也。气机翻运而为力者也。形器成局而为体者也。
定与局相类也。性理形器以相类而定局于上下。截然而不乱也。妙与运相类也。心神气机以相类而妙运于中间。变动而不居也。
性理心神之定之妙。为体为用准则而主宰。同位上也。气机形器之运之局。为力为体功用而物质。同位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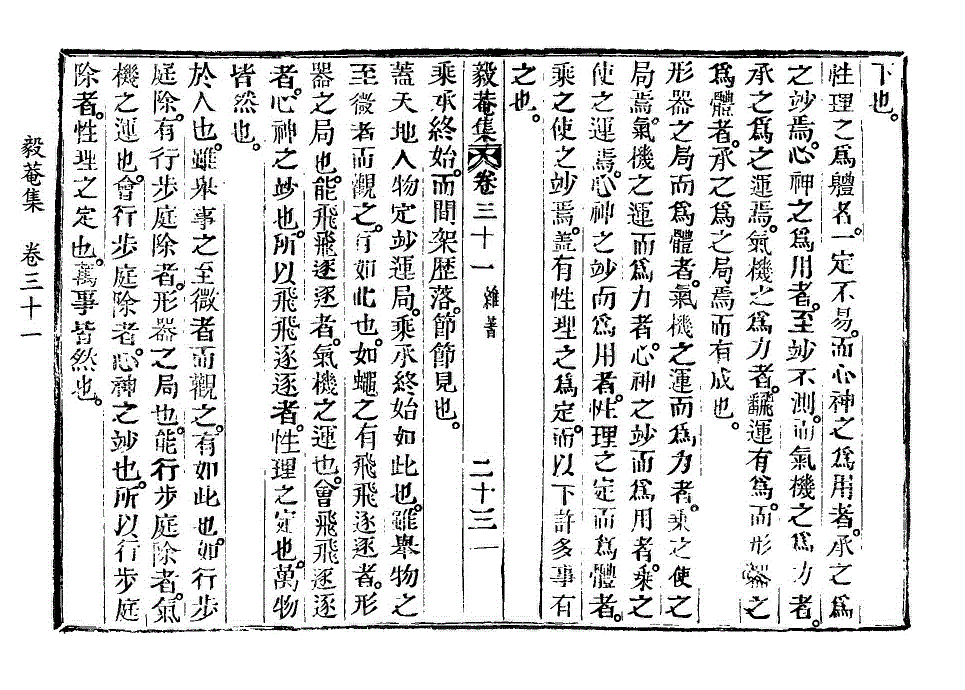 下也。
下也。性理之为体者。一定不易。而心神之为用者。承之为之妙焉。心神之为用者。至妙不测。而气机之为力者。承之为之运焉。气机之为力者。翻运有为。而形器之为体者。承之为之局焉而有成也。
形器之局而为体者。气机之运而为力者。乘之使之局焉。气机之运而为力者。心神之妙而为用者。乘之使之运焉。心神之妙而为用者。性理之定而为体者。乘之使之妙焉。盖有性理之为定。而以下许多事有之也。
乘承终始。而间架历落。节节见也。
盖天地人物定妙运局。乘承终始如此也。虽举物之至微者而观之。有如此也。如蝇之有飞飞逐逐者。形器之局也。能飞飞逐逐者。气机之运也。会飞飞逐逐者。心神之妙也。所以飞飞逐逐者。性理之定也。万物皆然也。
于人也。虽举事之至微者而观之。有如此也。如行步庭除。有行步庭除者。形器之局也。能行步庭除者。气机之运也。会行步庭除者。心神之妙也。所以行步庭除者。性理之定也。万事皆然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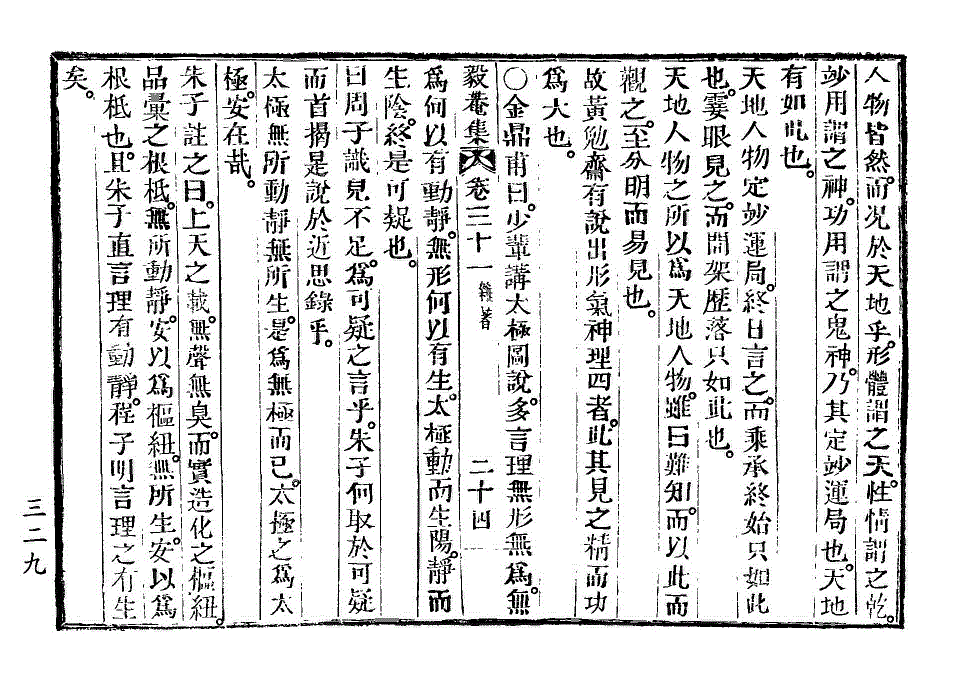 人物皆然。而况于天地乎。形体谓之天。性情谓之乾。妙用谓之神。功用谓之鬼神。乃其定妙运局也。天地有如此也。
人物皆然。而况于天地乎。形体谓之天。性情谓之乾。妙用谓之神。功用谓之鬼神。乃其定妙运局也。天地有如此也。天地人物定妙运局。终日言之。而乘承终始只如此也。霎眼见之。而间架历落只如此也。
天地人物之所以为天地人物。虽曰难知。而以此而观之。至分明而易见也。
故黄勉斋有说出形气神理四者。此其见之精而功为大也。
○金鼎甫曰。少辈讲太极图说。多言理无形无为。无为何以有动静。无形何以有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终是可疑也。
曰周子识见不足。为可疑之言乎。朱子何取于可疑而首揭是说于近思录乎。
太极无所动静无所生。是为无极而已。太极之为太极。安在哉。
朱子注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无所动静。安以为枢纽。无所生。安以为根柢也。且朱子直言理有动静。程子明言理之有生矣。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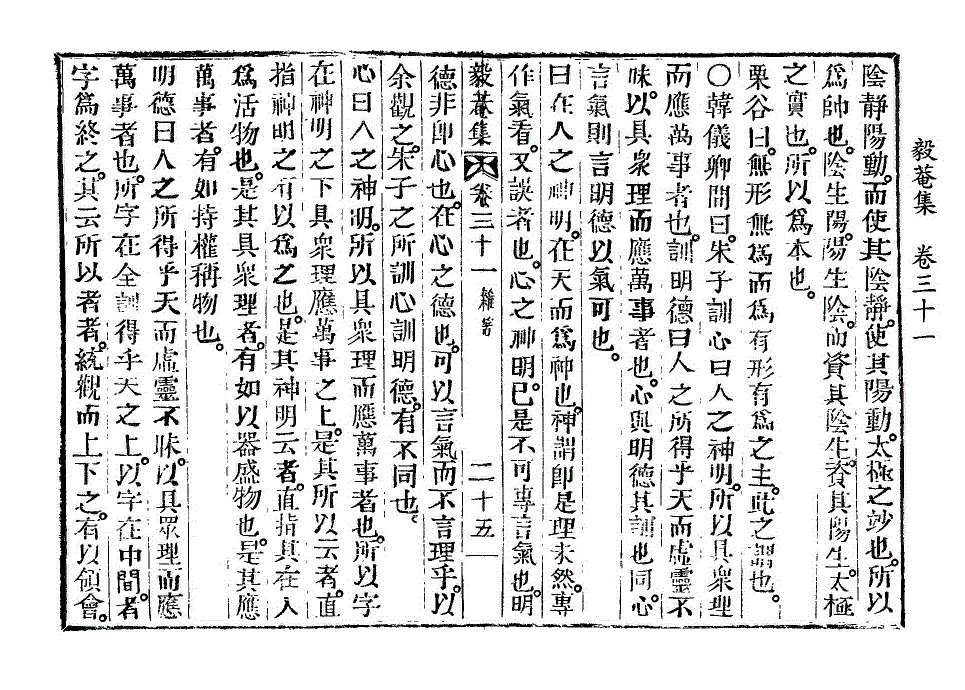 阴静阳动。而使其阴静。使其阳动。太极之妙也。所以为帅也。阴生阳。阳生阴。而资其阴生。资其阳生。太极之实也。所以为本也。
阴静阳动。而使其阴静。使其阳动。太极之妙也。所以为帅也。阴生阳。阳生阴。而资其阴生。资其阳生。太极之实也。所以为本也。栗谷曰。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此之谓也。
○韩仪卿问曰。朱子训心曰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训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心与明德其训也同。心言气则言明德以气可也。
曰在人之神明。在天而为神也。神谓即是理未然。专作气看。又误者也。心之神明。已是不可专言气也。明德非即心也。在心之德也。可以言气而不言理乎。以余观之。朱子之所训心训明德。有不同也。
心曰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所以字在神明之下具众理应万事之上。是其所以云者。直指神明之有以为之也。是其神明云者。直指其在人为活物也。是其具众理者。有如以器盛物也。是其应万事者。有如持权称物也。
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所字在全训得乎天之上。以字在中间。者字为终之。其云所以者者。统观而上下之。有以领会。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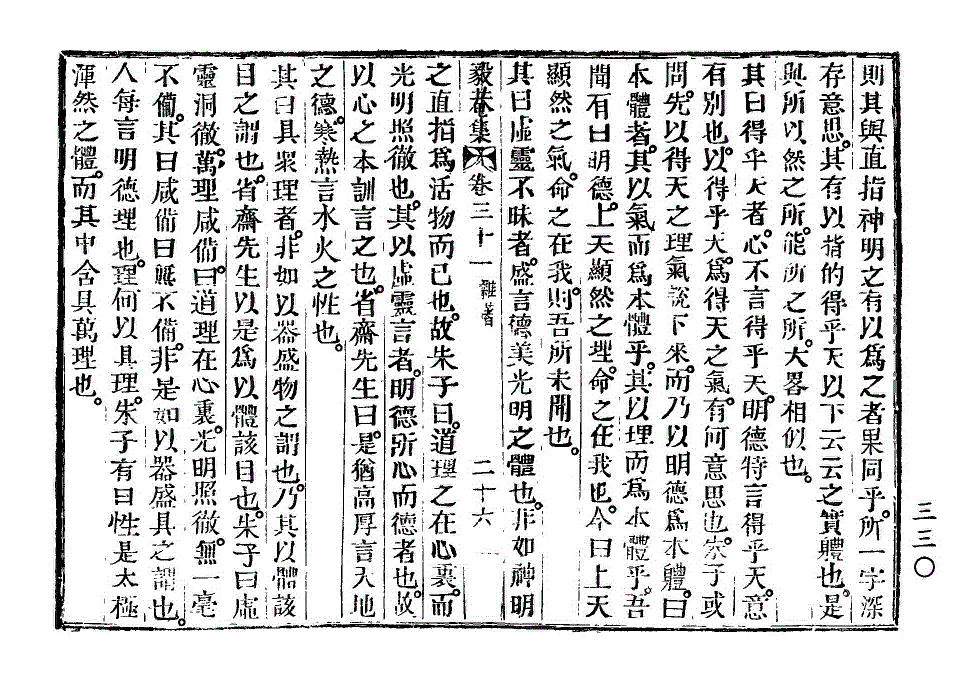 则其与直指神明之有以为之者果同乎。所一字深存意思。其有以指的得乎天以下云云之实体也。是与所以然之所。能所之所。大略相似也。
则其与直指神明之有以为之者果同乎。所一字深存意思。其有以指的得乎天以下云云之实体也。是与所以然之所。能所之所。大略相似也。其曰得乎天者。心不言得乎天。明德特言得乎天。意有别也。以得乎天。为得天之气。有何意思也。朱子或问。先以得天之理气说下来。而乃以明德为本体。曰本体者。其以气而为本体乎。其以理而为本体乎。吾闻有曰明德。上天显然之理。命之在我也。今曰上天显然之气。命之在我。则吾所未闻也。
其曰虚灵不昧者。盛言德美光明之体也。非如神明之直指为活物而已也。故朱子曰。道理之在心里。而光明照彻也。其以虚灵言者。明德所心而德者也。故以心之本训言之也。省斋先生曰。是犹高厚言天地之德。寒热言水火之性也。
其曰具众理者。非如以器盛物之谓也。乃其以体该目之谓也。省斋先生以是为以体该目也。朱子曰虚灵洞彻。万理咸备。曰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无一毫不备。其曰咸备曰无不备。非是如以器盛具之谓也。人每言明德理也。理何以具理。朱子有曰性是太极浑然之体。而其中含具万理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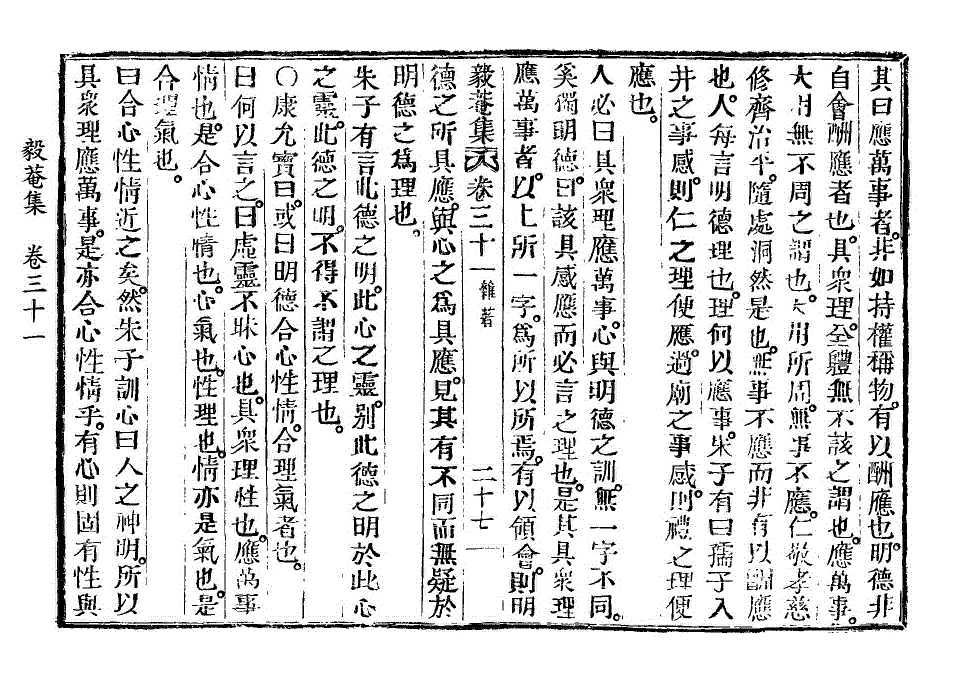 其曰应万事者。非如持权称物。有以酬应也。明德非自会酬应者也。具众理。全体无不该之谓也。应万事。大用无不周之谓也。大用所周。无事不应。仁敬孝慈修齐治平。随处洞然是也。无事不应而非有以酬应也。人每言明德理也。理何以应事。朱子有曰孺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过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也。
其曰应万事者。非如持权称物。有以酬应也。明德非自会酬应者也。具众理。全体无不该之谓也。应万事。大用无不周之谓也。大用所周。无事不应。仁敬孝慈修齐治平。随处洞然是也。无事不应而非有以酬应也。人每言明德理也。理何以应事。朱子有曰孺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过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也。人必曰其众理应万事。心与明德之训。无一字不同。奚独明德。曰该具感应而必言之理也。是其具众理应万事者。以上所一字。为所以所焉。有以领会。则明德之所具应。与心之为具应。见其有不同而无疑于明德之为理也。
朱子有言此德之明。此心之灵。别此德之明于此心之灵。此德之明。不得不谓之理也。
○康允宝曰。或曰明德合心性情。合理气者也。
曰何以言之。曰虚灵不昧心也。具众理性也。应万事情也。是合心性情也。心气也。性理也。情亦是气也。是合理气也。
曰合心性情近之矣。然朱子训心曰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应万事。是亦合心性情乎。有心则固有性与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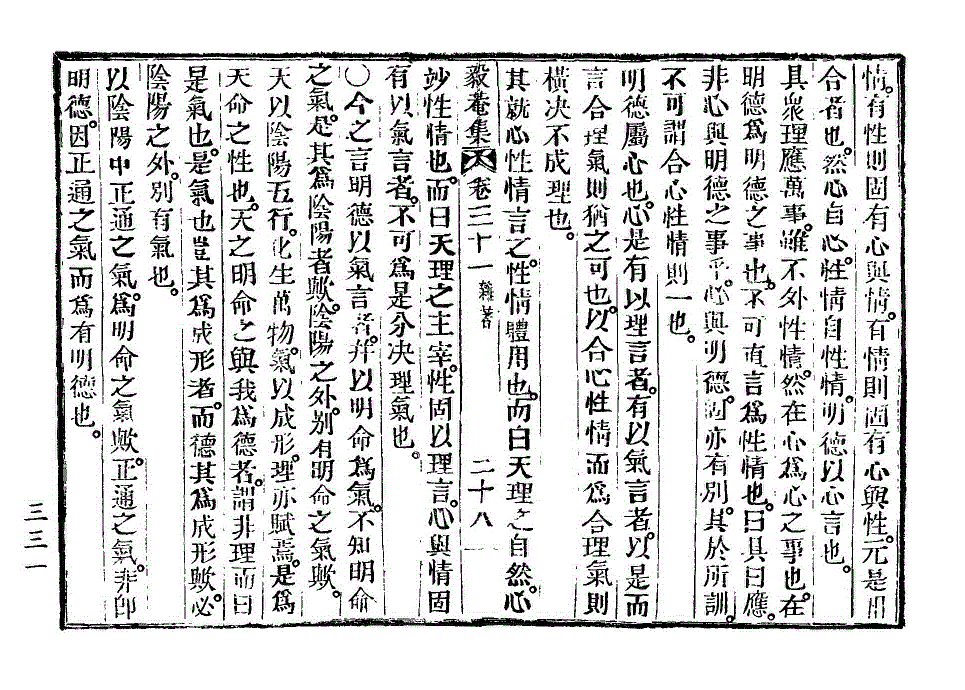 情。有性则固有心与情。有情则固有心与性。元是用合者也。然心自心。性情自性情。明德以心言也。
情。有性则固有心与情。有情则固有心与性。元是用合者也。然心自心。性情自性情。明德以心言也。具众理应万事。虽不外性情。然在心为心之事也。在明德为明德之事也。不可直言为性情也。曰具曰应。非心与明德之事乎。心与明德。固亦有别。其于所训。不可谓合心性情则一也。
明德属心也。心是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以是而言合理气则犹之可也。以合心性情而为合理气则横决不成理也。
其就心性情言之。性情体用也。而白天理之自然。心妙性情也。而曰天理之主宰。性固以理言。心与情固有以气言者。不可为是分决理气也。
○今之言明德以气言者。并以明命为气。不知明命之气。是其为阴阳者欤。阴阳之外。别有明命之气欤。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为天命之性也。天之明命之与我为德者。谓非理而曰是气也。是气也岂其为成形者。而德其为成形欤。必阴阳之外。别有气也。
以阴阳中正通之气。为明命之气欤。正通之气。非即明德。因正通之气而为有明德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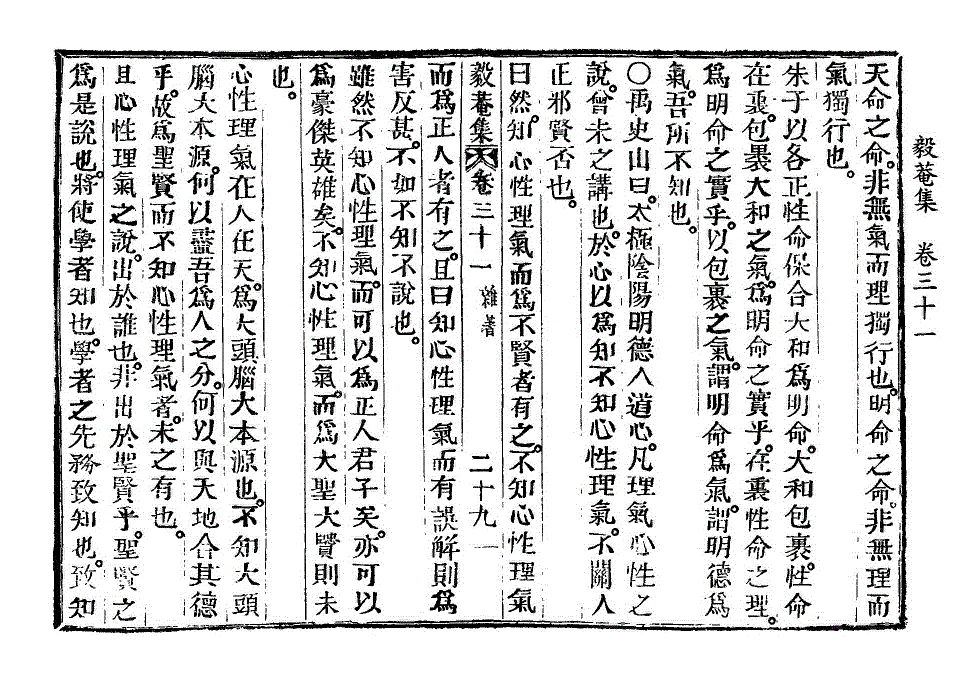 天命之命。非无气而理独行也。明命之命。非无理而气独行也。
天命之命。非无气而理独行也。明命之命。非无理而气独行也。朱子以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为明命。大和包裹。性命在里。包裹大和之气。为明命之实乎。在里性命之理。为明命之实乎。以包裹之气。谓明命为气。谓明德为气。吾所不知也。
○禹史山曰。太极阴阳明德人道心。凡理气心性之说。曾未之讲也。于心以为知不知心性理气。不关人正邪贤否也。
曰然。知心性理气而为不贤者有之。不知心性理气而为正人者有之。且曰知心性理气而有误解则为害反甚。不如不知不说也。
虽然不知心性理气。而可以为正人君子矣。亦可以为豪杰英雄矣。不知心性理气。而为大圣大贤则未也。
心性理气在人在天。为大头脑大本源也。不知大头脑大本源。何以尽吾为人之分。何以与天地合其德乎。故为圣贤而不知心性理气者。未之有也。
且心性理气之说。出于谁也。非出于圣贤乎。圣贤之为是说也。将使学者知也。学者之先务致知也。致知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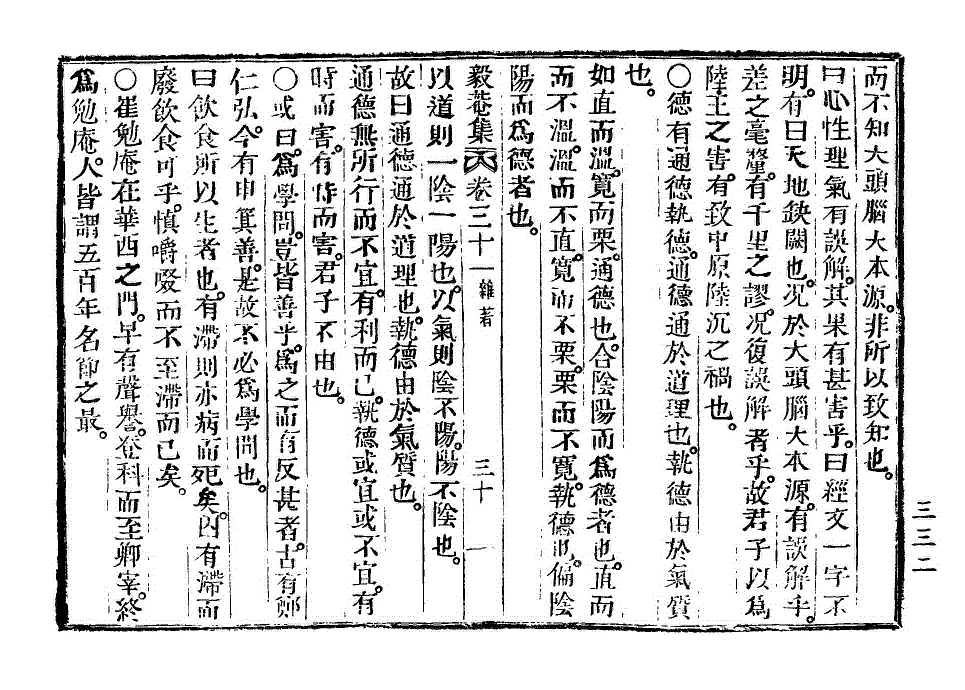 而不知大头脑大本源。非所以致知也。
而不知大头脑大本源。非所以致知也。曰心性理气有误解。其果有甚害乎。曰经文一字不明。有曰天地缺阙也。况于大头脑大本源。有误解乎。差之毫釐。有千里之谬。况复误解者乎。故君子以为陆,王之害。有致中原陆沉之祸也。
○德有通德执德。通德通于道理也。执德由于气质也。
如直而温。宽而栗。通德也。合阴阳而为德者也。直而而不温。温而不直。宽而不栗。栗而不宽。执德也。偏阴阳而为德者也。
以道则一阴一阳也。以气则阴不阳。阳不阴也。
故曰通德通于道理也。执德由于气质也。
通德无所行而不宜。有利而已。执德或宜或不宜。有时而害。有恃而害。君子不由也。
○或曰。为学问。岂皆善乎。为之而有反甚者。古有郑仁弘。今有申箕善。是故不必为学问也。
曰饮食所以生者也。有滞则亦病而死矣。囚有滞而废饮食可乎。慎嚼啜而不至滞而已矣。
○崔勉庵在华西之门。早有声誉。登科而至卿宰。终为勉庵。人皆谓五百年名节之最。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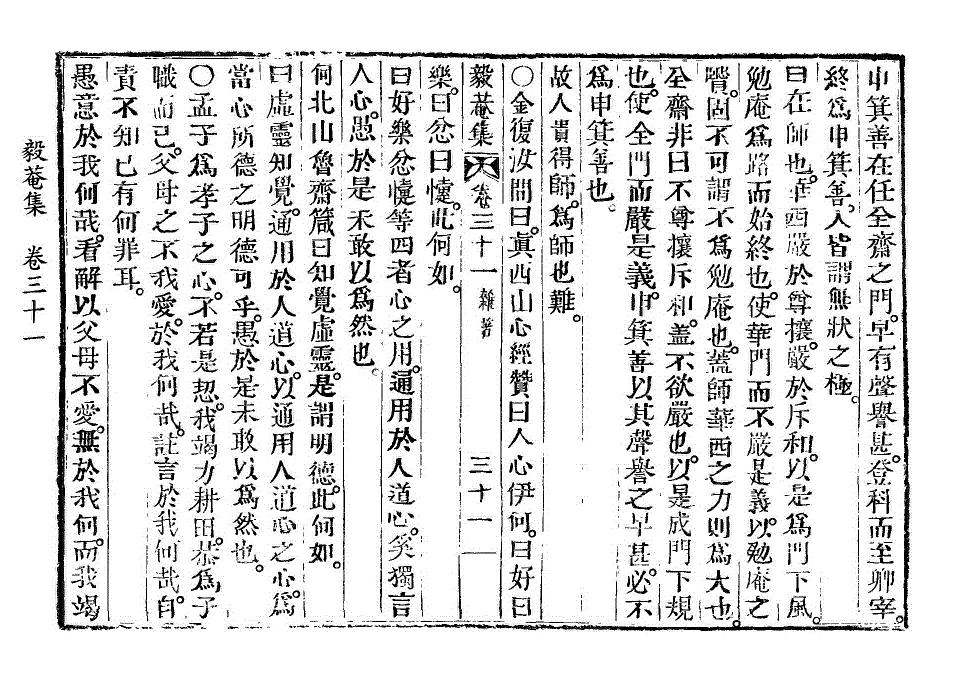 申箕善在任全斋之门。早有声誉甚。登科而至卿宰。终为申箕善。人皆谓无状之极。
申箕善在任全斋之门。早有声誉甚。登科而至卿宰。终为申箕善。人皆谓无状之极。曰在师也。华西严于尊攘。严于斥和。以是为门下风。勉庵为路而始终也。使华门而不严是义。以勉庵之贤。固不可谓不为勉庵也。盖师华西之力则为大也。全斋非曰不尊攘斥和。盖不欲严也。以是成门下规也。使全门而严是义。申箕善以其声誉之早甚。必不为申箕善也。
故人贵得师。为师也难。
○金复汝问曰。真西山心经赞曰人心伊何。曰好曰乐。曰忿曰懥。此何如。
曰好乐忿懥等四者心之用。通用于人道心。奚独言人心。愚于是未敢以为然也。
何北山鲁斋箴曰知觉虚灵。是谓明德。此何如。
曰虚灵知觉。通用于人道心。以通用人道心之心。为当心所德之明德可乎。愚于是未敢以为然也。
○孟子为孝子之心。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恭为子职而已。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注言于我何哉。自责不知己有何罪耳。
愚意于我何哉。看解以父母不爱。无于我何。而我竭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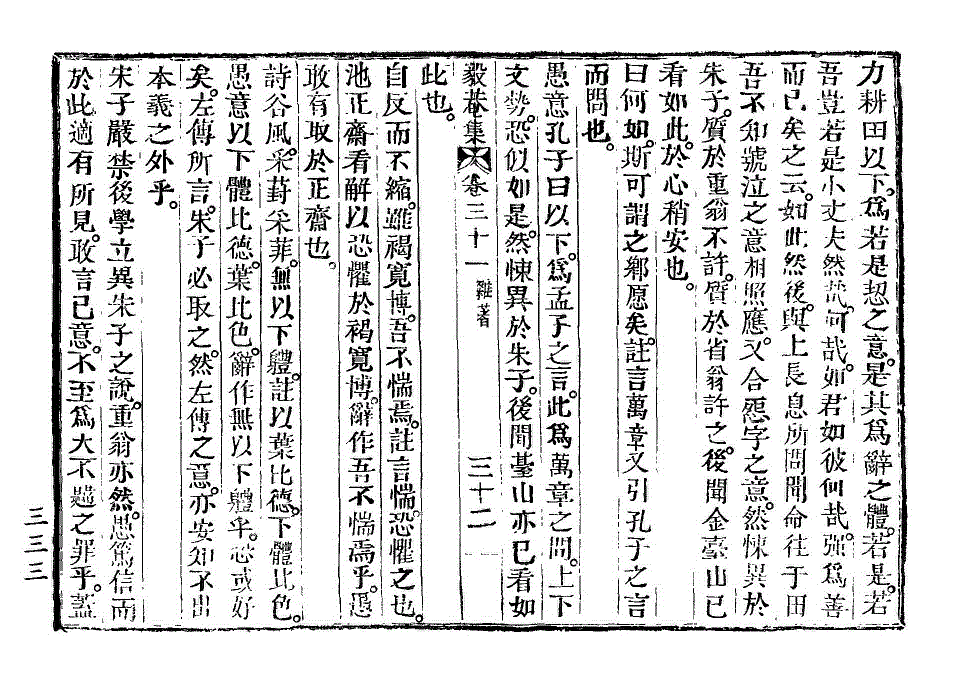 力耕田以下。为若是恝之意。是其为辞之体。若是。若吾岂若是小丈夫然哉。何哉。如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之云。如此然后。与上长息所问闻命往于田吾不知号泣之意相照应。又合怨字之意。然悚异于朱子。质于重翁不许。质于省翁许之。后闻金台山已看如此。于心稍安也。
力耕田以下。为若是恝之意。是其为辞之体。若是。若吾岂若是小丈夫然哉。何哉。如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之云。如此然后。与上长息所问闻命往于田吾不知号泣之意相照应。又合怨字之意。然悚异于朱子。质于重翁不许。质于省翁许之。后闻金台山已看如此。于心稍安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愿矣。注言万章又引孔子之言而问也。
愚意孔子曰以下。为孟子之言。此为万章之问。上下文势。恐似如是。然悚异于朱子。后闻台山亦已看如此也。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注言惴。恐惧之也。池正斋看解以恐惧于褐宽博。辞作吾不惴焉乎。愚敢有取于正斋也。
诗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注以叶比德。下体比色。愚意以下体比德。叶比色。辞作无以下体乎。恐或好矣。左传所言。朱子必取之。然左传之意。亦安知不出本义之外乎。
宋子严禁后学立异朱子之说。重翁亦然。愚笃信而于此适有所见。敢言已意。不至为大不韪之罪乎。盖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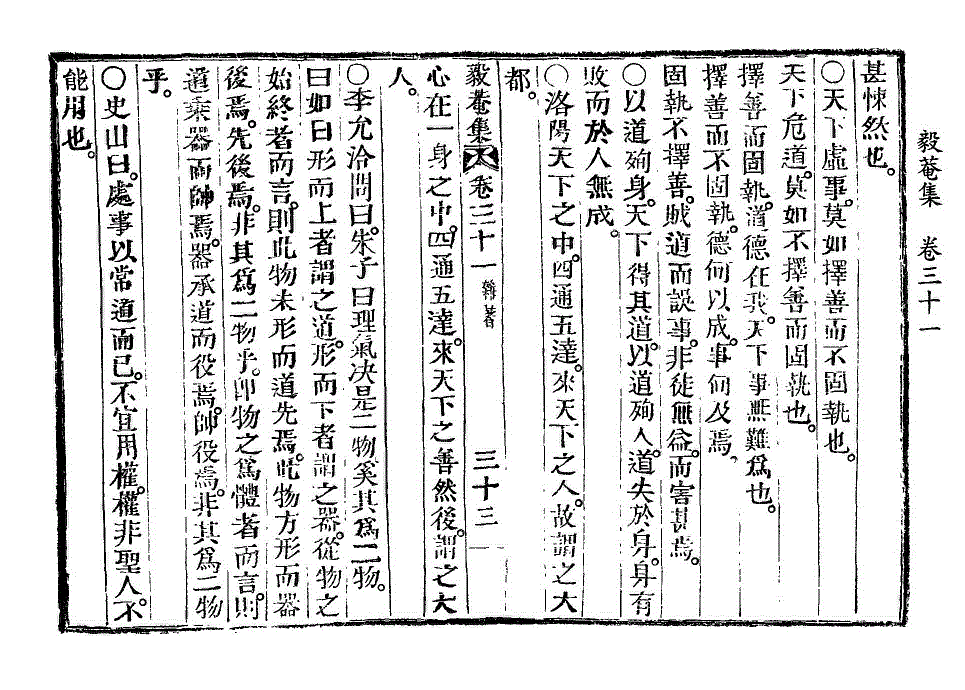 甚悚然也。
甚悚然也。○天下虚事。莫如择善而不固执也。
天下危道。莫如不择善而固执也。
择善而固执。道德在我。天下事无难为也。
择善而不固执。德何以成。事何及焉。
固执不择善。贼道而误事。非徒无益。而害甚焉。
○以道殉身。天下得其道。以道殉人。道失于身。身有败而于人无成。
○洛阳天下之中。四通五达。来天下之人。故谓之大都。
心在一身之中。四通五达。来天下之善然后。谓之大人。
○李允洽问曰。朱子曰理气决是二物奚其为二物。
曰如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物之始终者而言。则此物未形而道先焉。此物方形而器后焉。先后焉。非其为二物乎。即物之为体者而言。则道乘器而帅焉。器承道而役焉。帅役焉。非其为二物乎。
○史山曰。处事以常道而已。不宜用权。权非圣人。不能用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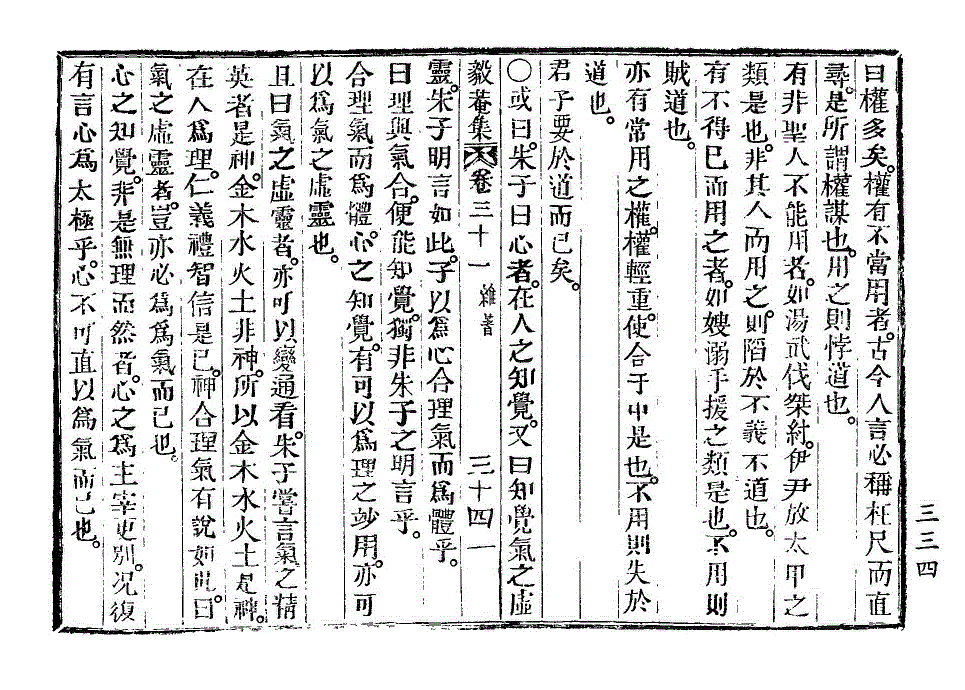 曰权多矣。权有不当用者。古今人言必称枉尺而直寻。是所谓权谋也。用之则悖道也。
曰权多矣。权有不当用者。古今人言必称枉尺而直寻。是所谓权谋也。用之则悖道也。有非圣人不能用者。如汤武伐桀纣。伊尹放太甲之类是也。非其人而用之。则陷于不义不道也。
有不得已而用之者。如嫂溺手援之类是也。不用则贼道也。
亦有常用之权。权轻重。使合于中是也。不用则失于道也。
君子要于道而已矣。
○或曰。朱子曰心者。在人之知觉。又曰知觉气之虚灵。朱子明言如此。子以为心合理气而为体乎。
曰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独非朱子之明言乎。
合理气而为体。心之知觉。有可以为理之妙用。亦可以为气之虚灵也。
且曰气之虚灵者。亦可以变通看。朱子尝言气之精英者是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金木水火土是神。在人为理。仁义礼智信是已。神合理气有说如此。曰气之虚灵者。岂亦必为为气而已也。
心之知觉。非是无理而然者。心之为主宰更别。况复有言心为太极乎。心不可直以为气而已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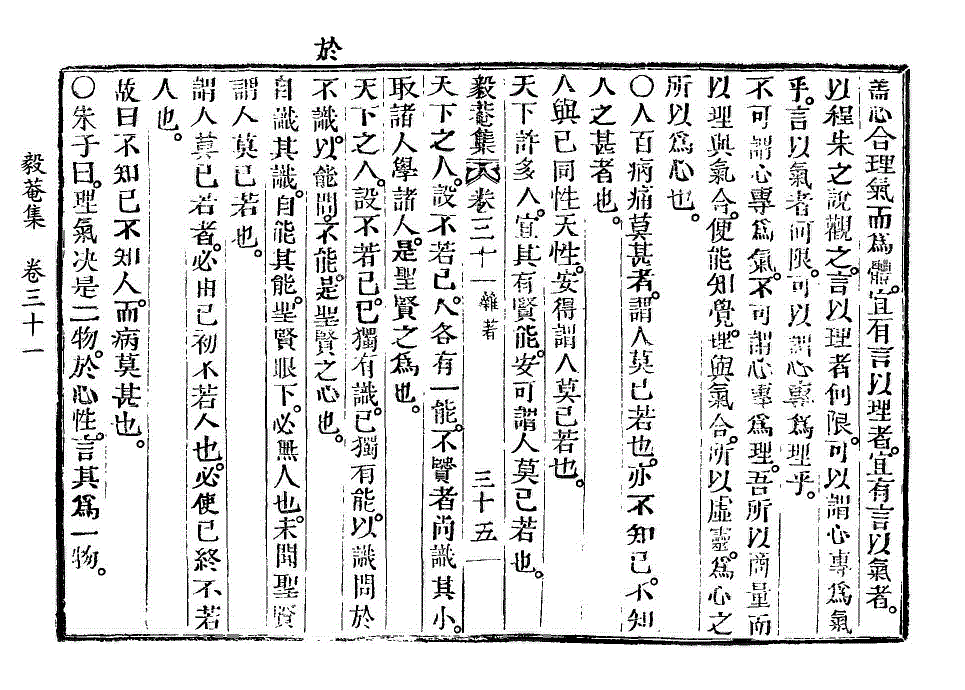 盖心合理气而为体。宜有言以理者。宜有言以气者。
盖心合理气而为体。宜有言以理者。宜有言以气者。以程朱之说观之。言以理者何限。可以谓心专为气乎。言以气者何限。可以谓心专为理乎。
不可谓心专为气。不可谓心专为理。吾所以商量而以理与气合。便能知觉。理与气合。所以虚灵。为心之所以为心也。
○人百病痛莫甚者。谓人莫己若也。亦不知己。不知人之甚者也。
人与己同性天性。安得谓人莫己若也。
天下许多人。宜其有贤能。安可谓人莫己若也。
天下之人。设不若己。人各有一能。不贤者尚识其小。取诸人学诸人。是圣贤之为也。
天下之人。设不若己。己独有识。己独有能。以识问于不识。以能问于不能。是圣贤之心也。
自识其识。自能其能。圣贤眼下。必无人也。未闻圣贤谓人莫己若也。
谓人莫己若者。必由己初不若人也。必使己终不若人也。
故曰不知己不知人。而病莫甚也。
○朱子曰。理气决是二物。于心性。言其为一物。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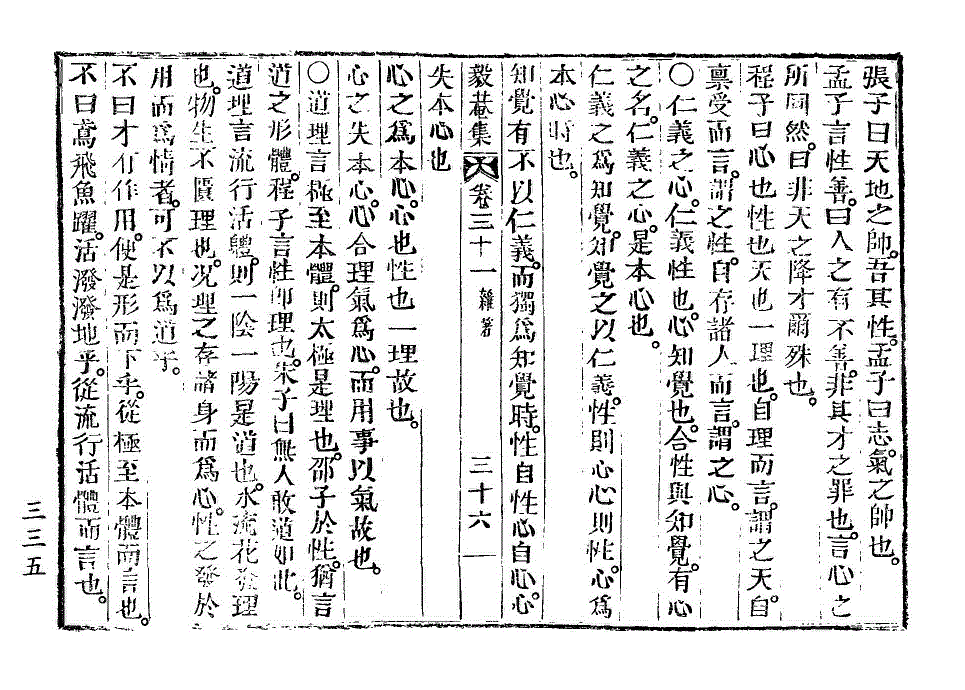 张子曰天地之帅。吾其性。孟子曰志。气之帅也。
张子曰天地之帅。吾其性。孟子曰志。气之帅也。孟子言性善。曰人之有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言心之所同然。曰非天之降才尔殊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
○仁义之心。仁义性也。心知觉也。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仁义之心。是本心也。
仁义之为知觉。知觉之以仁义。性则心心则性。心为本心时也。
知觉有不以仁义。而独为知觉时。性自性心自心。心失本心也。
心之为本心。心也性也一理故也。
心之失本心。心合理气为心。而用事以气故也。
○道理言极至本体。则太极是理也。邵子于性。犹言道之形体。程子言性即理也。朱子曰无人敢道如此。
道理言流行活体。则一阴一阳是道也。水流花发理也。物生不匮理也。况理之存诸身而为心。性之发于用而为情者。可不以为道乎。
不曰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乎。从极至本体而言也。不曰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乎。从流行活体而言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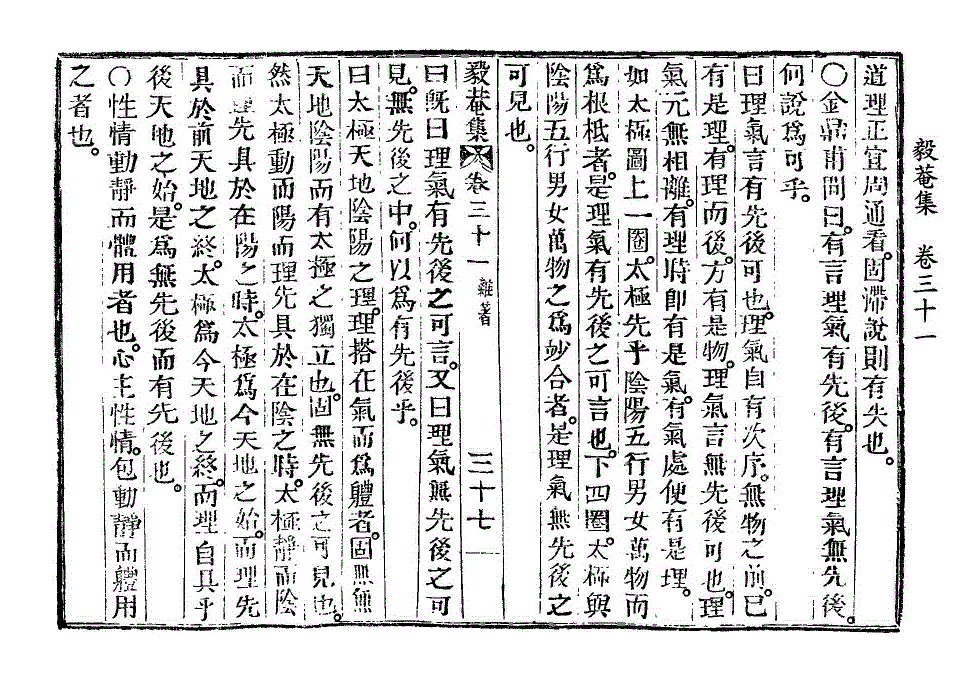 道理正宜周通看。固滞说则有失也。
道理正宜周通看。固滞说则有失也。○金鼎甫问曰。有言理气有先后。有言理气无先后。何说为可乎。
曰理气言有先后可也。理气自有次序。无物之前。已有是理。有理而后。方有是物。理气言无先后可也。理气元无相离。有理时即有是气。有气处便有是理。
如太极图上一圈。太极先乎阴阳五行男女万物而为根柢者。是理气有先后之可言也。下四圈。太极与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之为妙合者。是理气无先后之可见也。
曰既曰理气有先后之可言。又曰理气无先后之可见。无先后之中。何以为有先后乎。
曰太极天地阴阳之理。理搭在气而为体者。固无无天地阴阳而有太极之独立也。固无先后之可见也。然太极动而阳而理先具于在阴之时。太极静而阴而理先具于在阳之时。太极为今天地之始。而理先具于前天地之终。太极为今天地之终。而理自具乎后天地之始。是为无先后而有先后也。
○性情动静而体用者也。心主性情。包动静而体用之者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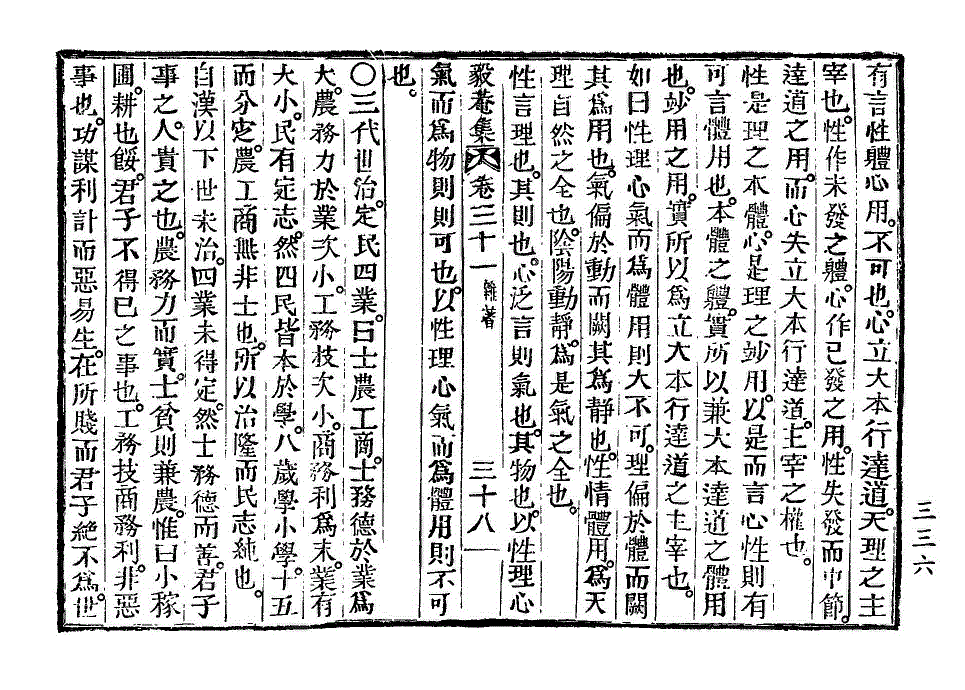 有言性体心用。不可也。心立大本行达道。天理之主宰也。性作未发之体。心作已发之用。性失发而中节。达道之用。而心失立大本行达道。主宰之权也。
有言性体心用。不可也。心立大本行达道。天理之主宰也。性作未发之体。心作已发之用。性失发而中节。达道之用。而心失立大本行达道。主宰之权也。性是理之本体。心是理之妙用。以是而言心性则有可言体用也。本体之体。实所以兼大本达道之体用也。妙用之用。实所以为立大本行达道之主宰也。
如曰性理心气而为体用则大不可。理偏于体而阙其为用也。气偏于动而阙其为静也。性情体用。为天理自然之全也。阴阳动静。为是气之全也。
性言理也。其则也。心泛言则气也。其物也。以性理心气而为物则则可也。以性理心气而为体用则不可也。
○三代世治。定民四业。曰士农工商。士务德于业为大。农务力于业次小。工务技次小。商务利为末。业有大小。民有定志。然四民皆本于学。八岁学小学。十五而分定。农工商无非士也。所以治隆而民志纯也。
自汉以下世未治。四业未得定。然士务德而善。君子事之。人贵之也。农务力而实。士贫则兼农。惟曰小稼圃。耕也馁。君子不得已之事也。工务技商务利。非恶事也。功谋利计而恶易生。在所贱而君子绝不为。世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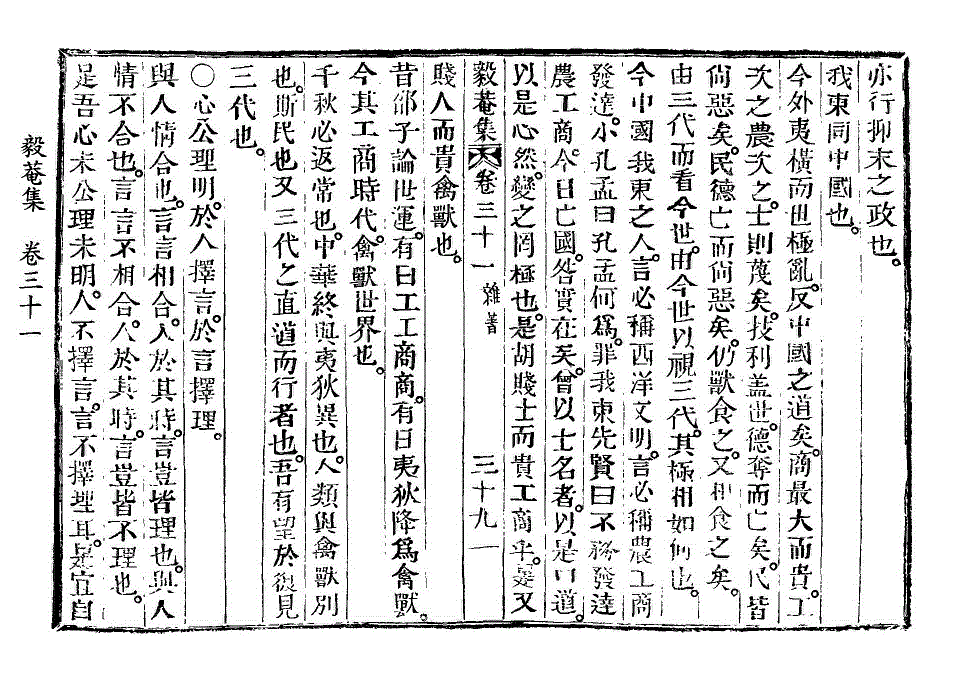 亦行抑末之政也。
亦行抑末之政也。我东同中国也。
今外夷横而世极乱。反中国之道矣。商最大而贵。工次之农次之。士则蔑矣。技利盖世。德夺而亡矣。民皆尚恶矣。民德亡而尚恶矣。仍兽食之。又相食之矣。
由三代而看今世。由今世以视三代。其极相如何也。
今中国我东之人。言必称西洋文明。言必称农工商发达。小孔孟曰孔孟何为。罪我东先贤曰不务发达农工商。今日亡国。咎实在矣。曾以士名者。以是口道。以是心然。变之罔极也。是胡贱士而贵工商乎。是又贱人而贵禽兽也。
昔邵子论世运。有曰工工商商。有日夷狄降为禽兽。今其工商时代。禽兽世界也。
千秋必返常也。中华终与夷狄异也。人类与禽兽别也。斯民也又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也。吾有望于复见三代也。
○心公理明。于人择言。于言择理。
与人情合也。言言相合。人于其时。言岂皆理也。与人情不合也。言言不相合。人于其时。言岂皆不理也。
是吾心未公理未明。人不择言。言不择理耳。是宜自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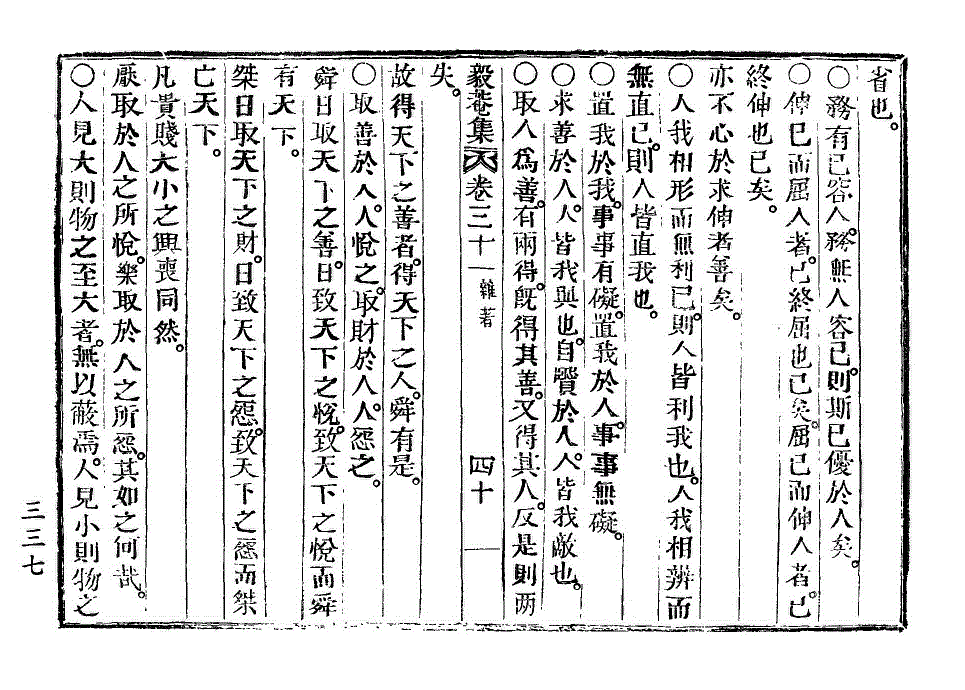 省也。
省也。○务有己容人。务无人容己。则斯己优于人矣。
○伸己而屈人者。己终屈也已矣。屈己而伸人者。己终伸也已矣。
亦不心于求伸者善矣。
○人我相形而无利己。则人皆利我也。人我相辨而无直己。则人皆直我也。
○置我于我。事事有碍。置我于人。事事无碍。
○求善于人。人皆我与也。自贤于人。人皆我敌也。
○取人为善。有两得。既得其善。又得其人。反是则两失。
故得天下之善者。得天下之人。舜有是。
○取善于人。人悦之。取财于人。人怨之。
舜日取天下之善。日致天下之悦。致天下之悦而舜有天下。
桀日取天下之财。日致天下之怨。致天下之怨而桀亡天下。
凡贵贱大小之兴丧同然。
厌取于人之所悦。乐取于人之所怨。其如之何哉。
○人见大则物之至大者。无以蔽焉。人见小则物之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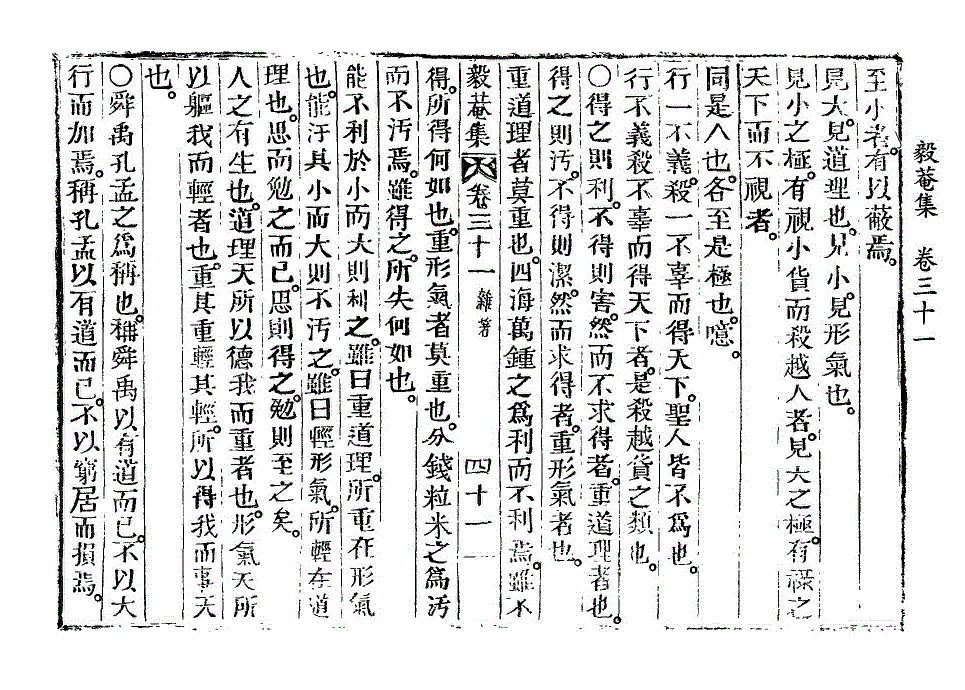 至小者。有以蔽焉。
至小者。有以蔽焉。见大。见道理也。见小。见形气也。
见小之极。有视小货而杀越人者。见大之极。有禄之天下而不视者。
同是人也。各至是极也。噫。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圣人皆不为也。
行不义杀不辜而得天下者。是杀越货之类也。
○得之则利。不得则害。然而不求得者。重道理者也。
得之则污。不得则洁。然而求得者。重形气者也。
重道理者莫重也。四海万钟之为利而不利焉。虽不得。所得何如也。重形气者莫重也。分钱粒米之为污而不污焉。虽得之。所失何如也。
能不利于小而大则利之。虽曰重道理。所重在形气也。能污其小而大则不污之。虽曰轻形气。所轻在道理也。思而勉之而已。思则得之。勉则至之矣。
人之有生也。道理天所以德我而重者也。形气天所以躯我而轻者也。重其重轻其轻。所以得我而事天也。
○舜禹孔孟之为称也。称舜禹以有道而已。不以大行而加焉。称孔孟以有道而已。不以穷居而损焉。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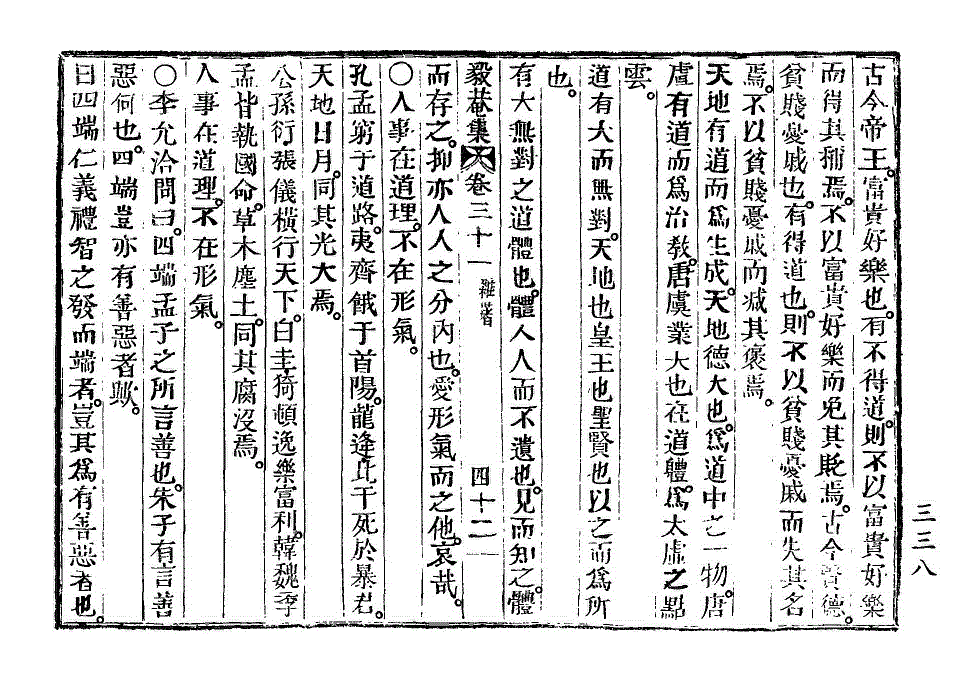 古今帝王。富贵好乐也。有不得道。则不以富贵好乐而得其称焉。不以富贵好乐而免其贬焉。古今贤德。贫贱忧戚也。有得道也。则不以贫贱忧戚而失其名焉。不以贫贱忧戚而减其褒焉。
古今帝王。富贵好乐也。有不得道。则不以富贵好乐而得其称焉。不以富贵好乐而免其贬焉。古今贤德。贫贱忧戚也。有得道也。则不以贫贱忧戚而失其名焉。不以贫贱忧戚而减其褒焉。天地有道而为生成。天地德大也。为道中之一物。唐虞有道而为治教。唐虞业大也在道体。为太虚之点云。
道有大而无对。天地也皇王也圣贤也以之而为所也。
有大无对之道体也。体人人而不遗也。见而知之。体而存之。抑亦人人之分内也。爱形气而之他。哀哉。
○人事在道理。不在形气。
孔孟穷于道路。夷齐饿于首阳。龙逄,比干死于暴君。天地日月。同其光大焉。
公孙衍,张仪横行天下。白圭,猗顿逸乐富利。韩魏季孟皆执国命。草木尘土。同其腐没焉。
人事在道理。不在形气。
○李允洽问曰。四端孟子之所言善也。朱子有言善恶何也。四端岂亦有善恶者欤。
曰四端仁义礼智之发而端者。岂其为有善恶者也。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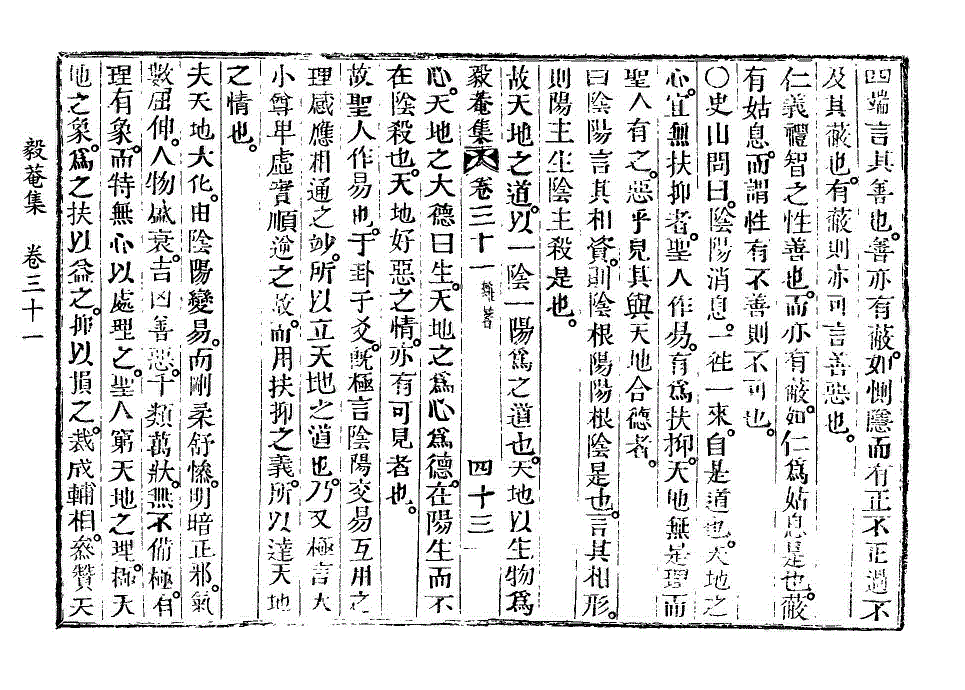 四端言其善也。善亦有蔽。如恻隐而有正不正过不及其蔽也。有蔽则亦可言善恶也。
四端言其善也。善亦有蔽。如恻隐而有正不正过不及其蔽也。有蔽则亦可言善恶也。仁义礼智之性善也。而亦有蔽。如仁为姑息是也。蔽有姑息。而谓性有不善则不可也。
○史山问曰。阴阳消息。一往一来。自是道也。天地之心。宜无扶抑者。圣人作易。有为扶抑。天地无是理而圣人有之。恶乎见其与天地合德者。
曰阴阳言其相资。则阴根阳阳根阴是也。言其相形。则阳主生阴主杀是也。
故天地之道。以一阴一阳为之道也。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为心为德。在阳生而不在阴杀也。天地好恶之情。亦有可见者也。
故圣人作易也。于卦于爻。既极言阴阳交易互用之理感应相通之妙。所以立天地之道也。乃又极言大小尊卑虚实顺逆之故。而用扶抑之义。所以达天地之情也。
夫天地大化。由阴阳变易。而刚柔舒惨。明暗正邪。气数屈伸。人物盛衰。吉凶善恶。千类万状。无不备极。有理有象。而特无心以处理之。圣人穷天地之理。极天地之象。为之扶以益之。抑以损之。裁成辅相。参赞天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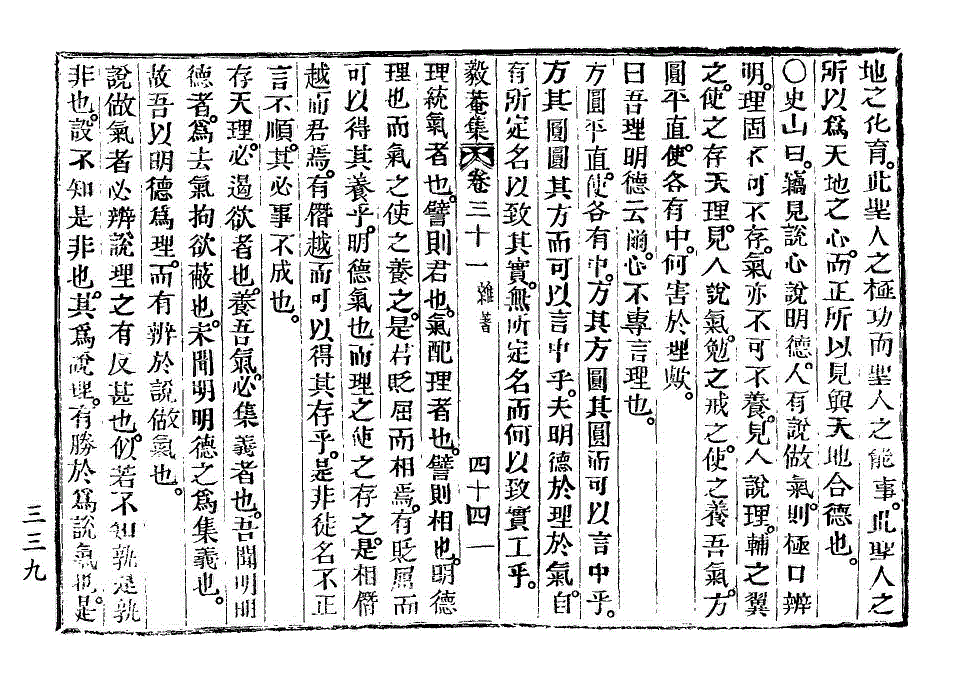 地之化育。此圣人之极功而圣人之能事。此圣人之所以为天地之心。而正所以见与天地合德也。
地之化育。此圣人之极功而圣人之能事。此圣人之所以为天地之心。而正所以见与天地合德也。○史山曰。窃见说心说明德。人有说做气。则极口辨明。理固不可不存。气亦不可不养。见人说理。辅之翼之。使之存天理。见人说气。勉之戒之。使之养吾气。方圆平直。使各有中。何害于理欤。
曰吾理明德云尔。心不专言理也。
方圆平直。使各有中。方其方圆其圆而可以言中乎。方其圆圆其方而可以言中乎。夫明德于理于气。自有所定名以致其实。无所定名而何以致实工乎。
理统气者也。譬则君也。气配理者也。譬则相也。明德理也而气之使之养之。是君贬屈而相焉。有贬屈而可以得其养乎。明德气也而理之使之存之。是相僭越而君焉。有僭越而可以得其存乎。是非徒名不正言不顺。其必事不成也。
存天理。必遏欲者也。养吾气。必集义者也。吾闻明明德者。为去气拘欲蔽也。未闻明明德之为集义也。
故吾以明德为理。而有辨于说做气也。
说做气者必辨说理之有反甚也。似若不知孰是孰非也。设不知是非也。其为说理。有胜于为说气也。是
毅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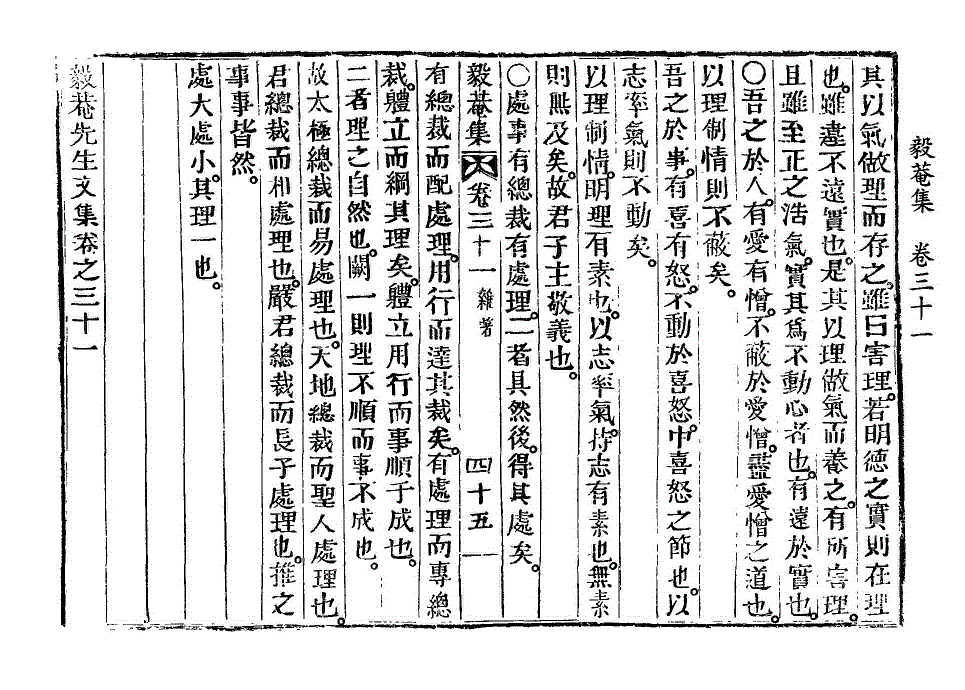 其以气做理而存之。虽曰害理。若明德之实则在理也。虽违不远实也。是其以理做气而养之。有所害理。且虽至正之浩气。实其为不动心者也。有远于实也。
其以气做理而存之。虽曰害理。若明德之实则在理也。虽违不远实也。是其以理做气而养之。有所害理。且虽至正之浩气。实其为不动心者也。有远于实也。○吾之于人。有爱有憎。不蔽于爱憎。尽爱憎之道也。以理制情则不蔽矣。
吾之于事。有喜有怒。不动于喜怒。中喜怒之节也。以志率气则不动矣。
以理制情。明理有素也。以志率气。持志有素也。无素则无及矣。故君子主敬义也。
○处事有总裁有处理。二者具然后。得其处矣。
有总裁而配处理。用行而达其裁矣。有处理而专总裁。体立而纲其理矣。体立用行而事顺于成也。
二者理之自然也。阙一则理不顺而事不成也。
故太极总裁而易处理也。天地总裁而圣人处理也。君总裁而相处理也。严君总裁而长子处理也。推之事事皆然。
处大处小。其理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