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杂著
杂著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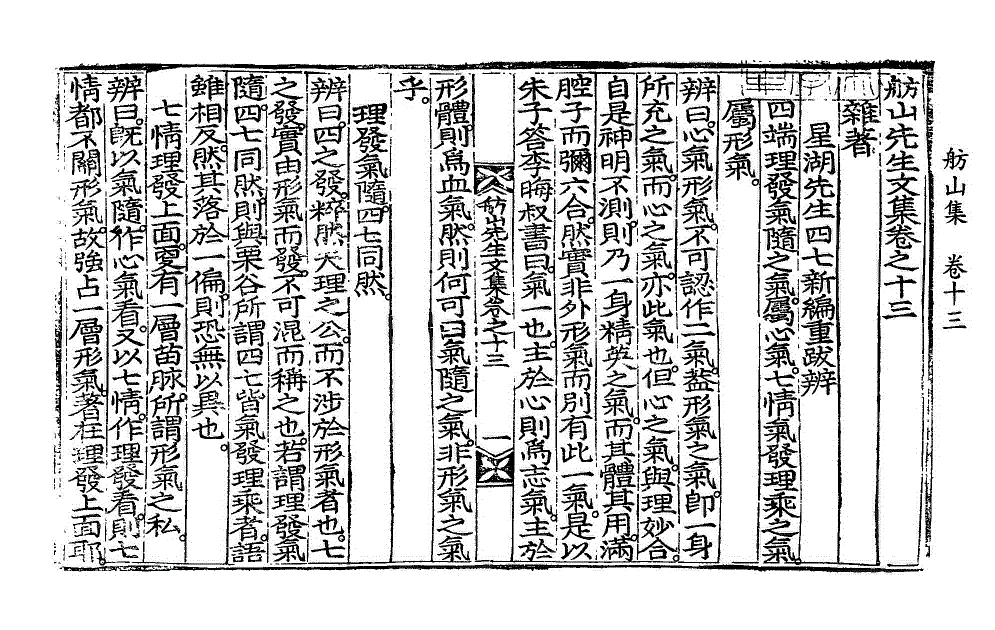 星湖先生四七新编重跋辨
星湖先生四七新编重跋辨四端理发气随之气。属心气。七情气发理乘之气。属形气。
辨曰。心气形气。不可认作二气。盖形气之气。即一身所充之气。而心之气。亦此气也。但心之气。与理妙合。自是神明不测。则乃一身精英之气。而其体其用。满腔子而弥六合。然实非外形气而别有此一气。是以朱子答李晦叔书曰。气一也。主于心则为志气。主于形体。则为血气。然则何可曰气随之气。非形气之气乎。
理发气随。四七同然。
辨曰。四之发。粹然天理之公。而不涉于形气者也。七之发。实由形气而发。不可混而称之也。若谓理发气随。四七同然。则与栗谷所谓四七皆气发理乘者。语虽相反。然其落于一偏。则恐无以异也。
七情理发上面。更有一层苗脉。所谓形气之私。
辨曰。既以气随。作心气看。又以七情。作理发看。则七情都不关形气。故强占一层形气。著在理发上面耶。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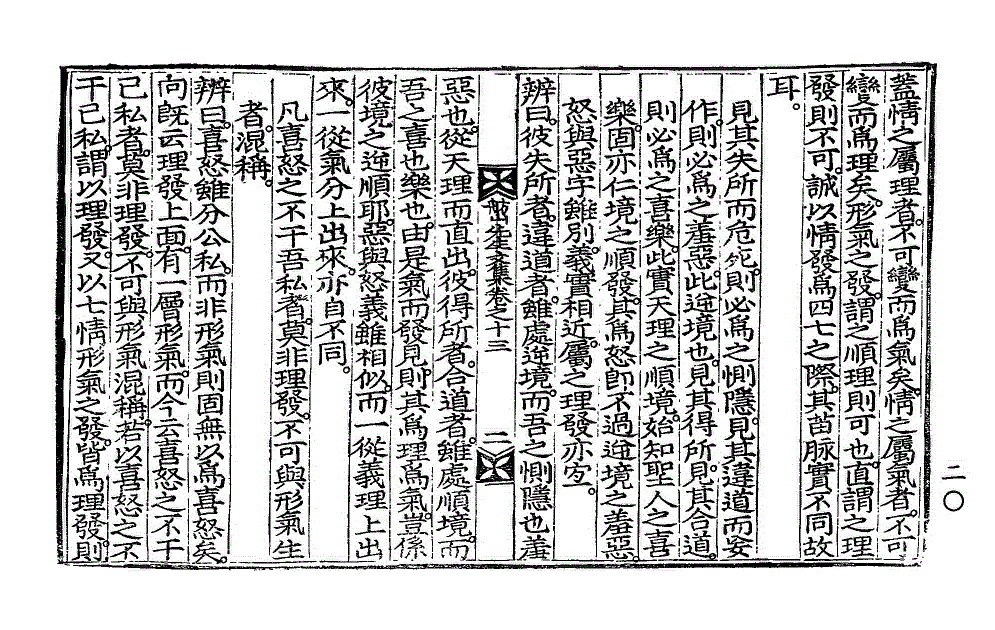 盖情之属理者。不可变而为气矣。情之属气者。不可变而为理矣。形气之发。谓之顺理则可也。直谓之理发则不可。诚以情发为四七之际。其苗脉实不同故耳。
盖情之属理者。不可变而为气矣。情之属气者。不可变而为理矣。形气之发。谓之顺理则可也。直谓之理发则不可。诚以情发为四七之际。其苗脉实不同故耳。见其失所而危死。则必为之恻隐。见其违道而妄作。则必为之羞恶。此逆境也。见其得所。见其合道。则必为之喜乐。此实天理之顺境。始知圣人之喜乐。固亦仁境之顺发。其为怒即不过逆境之羞恶。怒与恶字虽别。义实相近。属之理发亦宜。
辨曰。彼失所者。违道者。虽处逆境。而吾之恻隐也羞恶也。从天理而直出。彼得所者。合道者。虽处顺境。而吾之喜也乐也。由是气而发见。则其为理为气。岂系彼境之逆顺耶。恶与怒义虽相似。而一从义理上出来。一从气分上出来。亦自不同。
凡喜怒之不干吾私者。莫非理发。不可与形气生者。混称。
辨曰。喜怒虽分公私。而非形气则固无以为喜怒矣。向既云理发上面。有一层形气。而今云喜怒之不干己私者。莫非理发。不可与形气混称。若以喜怒之不干己私。谓以理发。又以七情形气之发。皆为理发。则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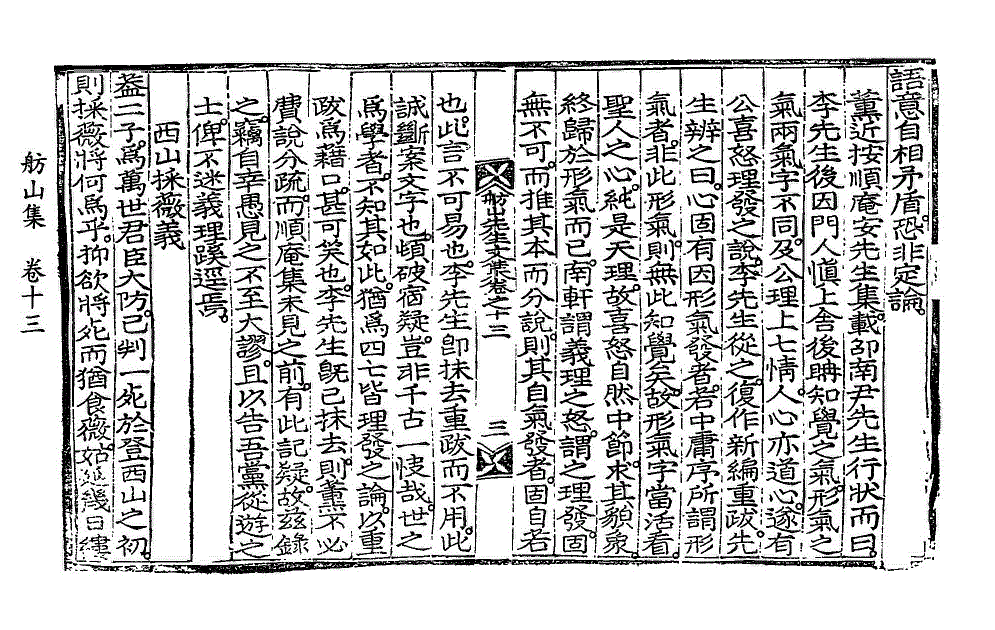 语意自相矛盾。恐非定论。
语意自相矛盾。恐非定论。薰近按顺庵安先生集。载邵南尹先生行状而曰。李先生后因门人慎上舍后聃知觉之气。形气之气两气字不同。及公理上七情。人心亦道心。遂有公喜怒理发之说。李先生从之。复作新编重跋。先生辨之曰。心固有因形气发者。若中庸序所谓形气者。非此形气。则无此知觉矣。故形气字当活看。圣人之心。纯是天理。故喜怒自然中节。求其貌象。终归于形气而已。南轩谓义理之怒。谓之理发。固无不可。而推其本而分说。则其自气发者。固自若也。此言不可易也。李先生即抹去重跋而不用。此诚断案文字也。顿破宿疑。岂非千古一快哉。世之为学者。不知其如此。犹为四七皆理发之论。以重跋为藉口。甚可笑也。李先生既已抹去。则薰不必费说分疏。而顺庵集未见之前。有此记疑。故玆录之。窃自幸愚见之不至大谬。且以告吾党从游之士。俾不迷义理蹊径焉。
西山采薇义
盖二子。为万世君臣大防。已判一死于登西山之初。则采薇将何为乎。抑欲将死而犹食薇。姑延几日缕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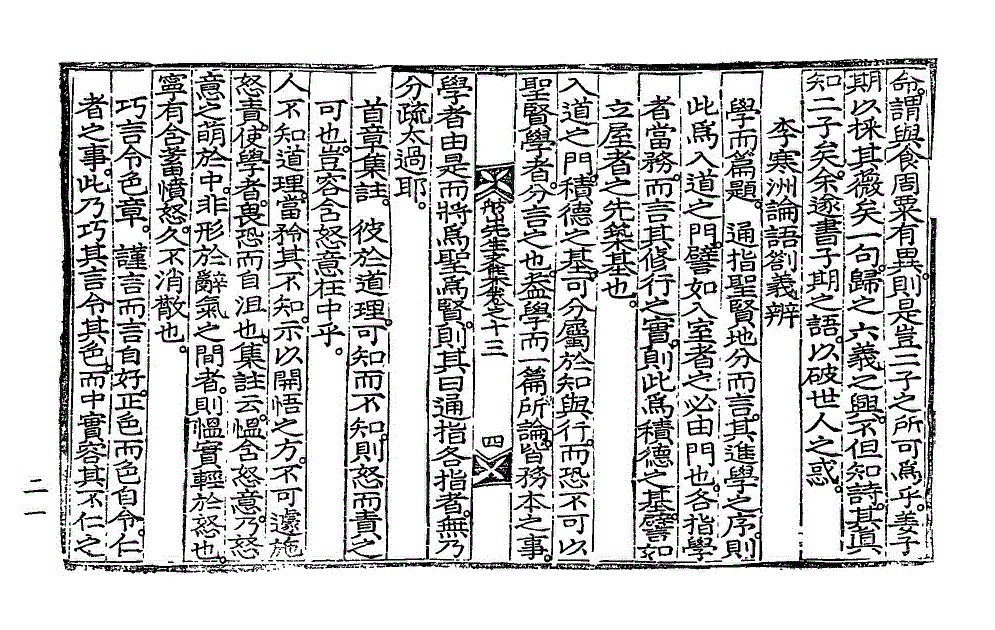 命。谓与食周粟有异。则是岂二子之所可为乎。姜子期以采其薇矣一句。归之六义之兴。不但知诗。其真知二子矣。余遂书子期之语。以破世人之惑。
命。谓与食周粟有异。则是岂二子之所可为乎。姜子期以采其薇矣一句。归之六义之兴。不但知诗。其真知二子矣。余遂书子期之语。以破世人之惑。李寒洲论语劄义辨
学而篇题。 通指圣贤地分而言。其进学之序。则此为入道之门。譬如入室者之必由门也。各指学者当务。而言其修行之实。则此为积德之基。譬如立屋者之先筑基也。
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可分属于知与行。而恐不可以圣贤学者。分言之也。盖学而一篇。所论。皆务本之事。学者由是而将为圣为贤。则其曰通指各指者。无乃分疏太过耶。
首章集注。 彼于道理。可知而不知。则怒而责之可也。岂容含怒意在中乎。
人不知道理。当矜其不知。示以开悟之方。不可遽施怒责。使学者。畏恐而自沮也。集注云。愠含怒意。乃怒意之萌于中。非形于辞气之间者。则愠实轻于怒也。宁有含蓄愤怒。久不消散也。
巧言令色章。 谨言而言自好。正色而色自令。仁者之事。此乃巧其言令其色。而中实容其不仁之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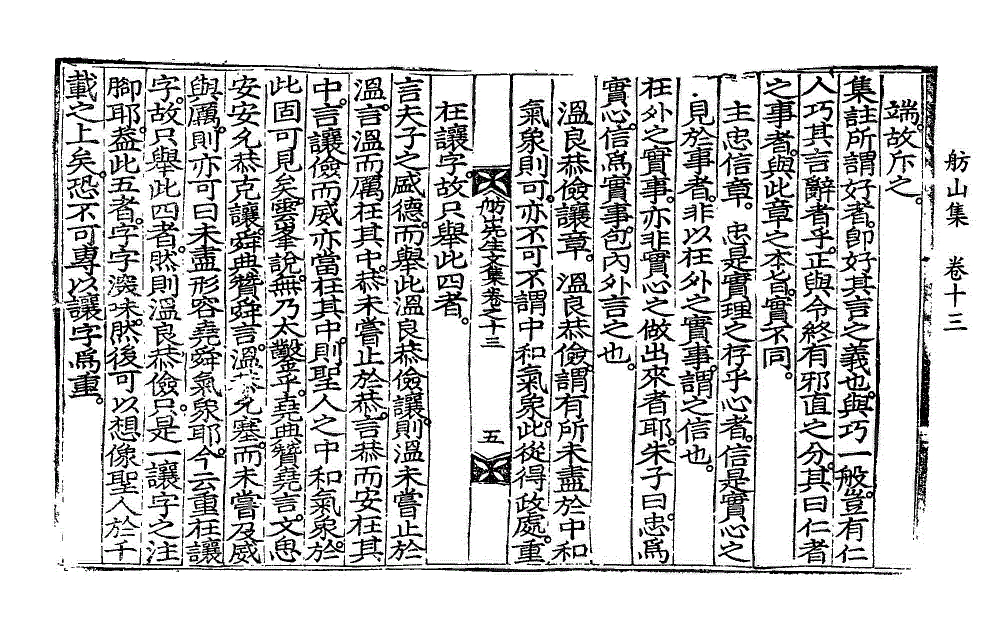 端。故斥之。
端。故斥之。集注所谓好者。即好其言之义也。与巧一般。岂有仁人巧其言辞者乎。正与令终有邪直之分。其曰仁者之事者。与此章之本旨。实不同。
主忠信章。 忠是实理之存乎心者。信是实心之见于事者。非以在外之实事。谓之信也。
在外之实事。亦非实心之做出来者耶。朱子曰。忠为实心。信为实事。包内外言之也。
温良恭俭让章。 温良恭俭。谓有所未尽于中和气象则可。亦不可不谓中和气象。此从得政处。重在让字。故只举此四者。
言夫子之盛德。而举此温良恭俭让。则温未尝止于温。言温而厉在其中。恭未尝止于恭。言恭而安在其中。言让俭而威亦当在其中。则圣人之中和气象。于此固可见矣。云峰说。无乃太凿乎。尧典赞尧言。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典赞舜言。温恭允塞。而未尝及威与厉。则亦可曰未尽形容尧舜气象耶。今云重在让字。故只举此四者。然则温良恭俭。只是一让字之注脚耶。盖此五者。字字深味。然后可以想像圣人于千载之上矣。恐不可专以让字为重。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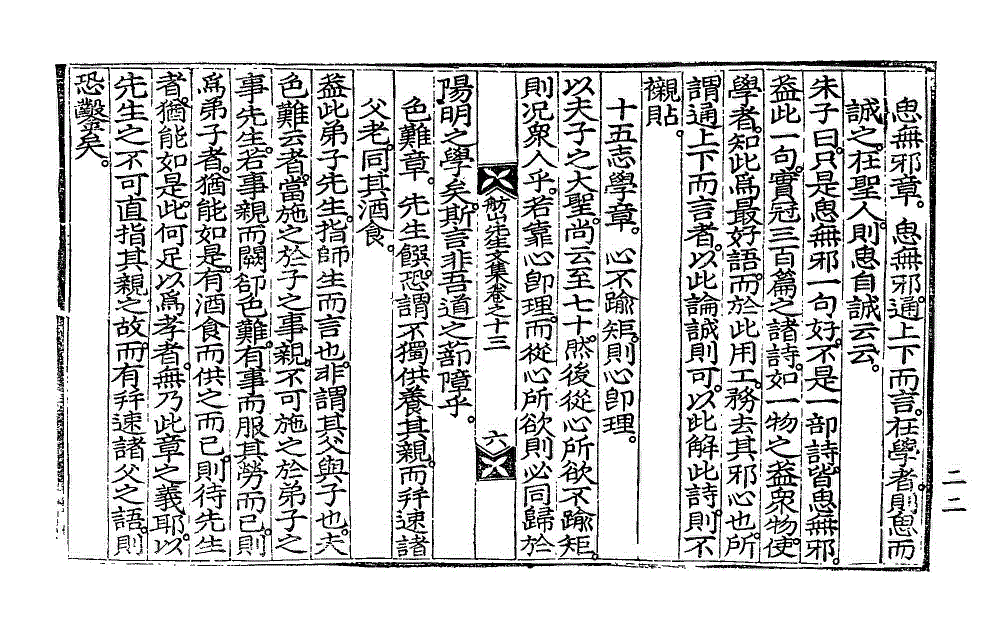 思无邪章。 思无邪。通上下而言。在学者。则思而诚之。在圣人。则思自诚云云。
思无邪章。 思无邪。通上下而言。在学者。则思而诚之。在圣人。则思自诚云云。朱子曰。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盖此一句。实冠三百篇之诸诗。如一物之盖众物。使学者。知此为最好语。而于此用工。务去其邪心也。所谓通上下而言者。以此论诚则可。以此解此诗。则不衬贴。
十五志学章。 心不踰矩。则心即理。
以夫子之大圣。尚云至七十。然后从心所欲不踰矩。则况众人乎。若靠心即理。而从心所欲则必同归于阳明之学矣。斯言非吾道之蔀障乎。
色难章。 先生馔。恐谓不独供养其亲。而并速诸父老。同其酒食。
盖此弟子先生。指师生而言也。非谓其父与子也。夫色难云者。当施之于子之事亲。不可施之于弟子之事先生。若事亲而阙却色难。有事而服其劳而已。则为弟子者。犹能如是。有酒食而供之而已。则待先生者。犹能如是。此何足以为孝者。无乃此章之义耶。以先生之不可直指其亲之故。而有并速诸父之语。则恐凿矣。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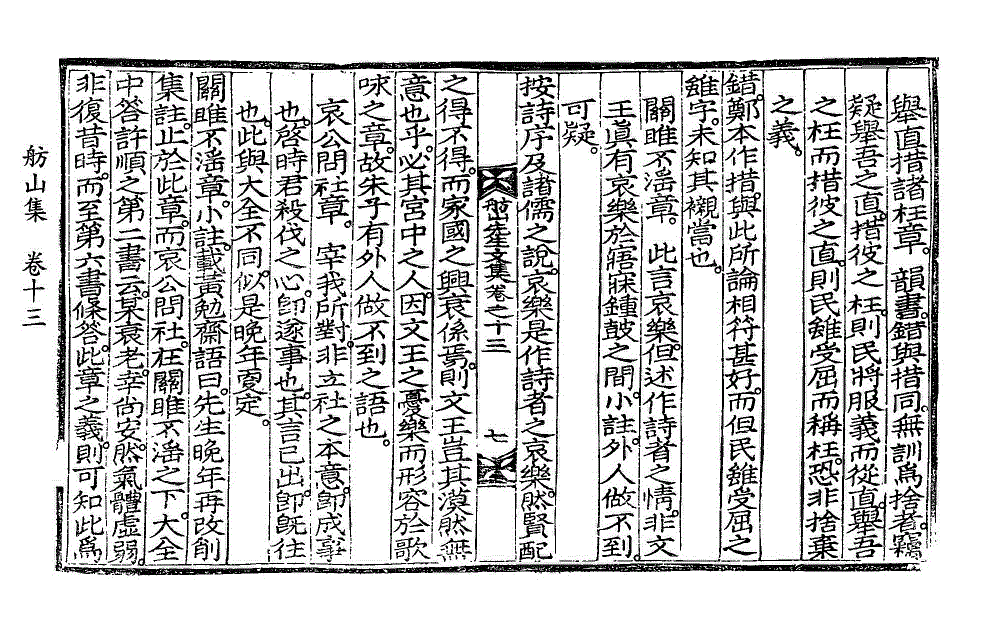 举直措诸枉章。 韵书。错与措同。无训为舍者。窃疑举吾之直。措彼之枉。则民将服义而从直。举吾之枉而措彼之直。则民虽受屈而称枉。恐非舍弃之义。
举直措诸枉章。 韵书。错与措同。无训为舍者。窃疑举吾之直。措彼之枉。则民将服义而从直。举吾之枉而措彼之直。则民虽受屈而称枉。恐非舍弃之义。错。郑本作措。与此所论相符甚好。而但民虽受屈之虽字。未知其衬当也。
关雎不淫章。 此言哀乐。但述作诗者之情。非文王真有哀乐于寤寐钟鼓之间。小注。外人做不到。可疑。
按诗序及诸儒之说。哀乐是作诗者之哀乐。然贤配之得不得。而家国之兴衰系焉。则文王岂其漠然无意也乎。必其宫中之人。因文王之忧乐而形容于歌咏之章。故朱子有外人做不到之语也。
哀公问社章。 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即成事也。启时君杀伐之心。即遂事也。其言已出。即既往也。此与大全不同。似是晚年更定。
关雎不淫章。小注。载黄勉斋语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注。止于此章。而哀公问社。在关雎不淫之下。大全中答许顺之第二书云。某衰老。幸尚安。然气体虚弱。非复昔时。而至第六书条答。此章之义。则可知此为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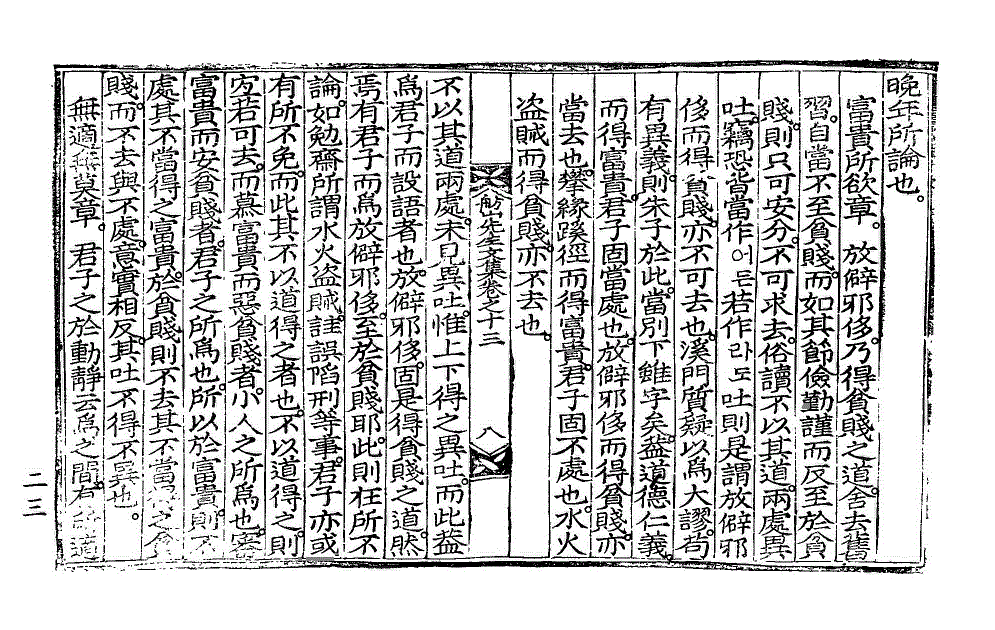 晚年所论也。
晚年所论也。富贵所欲章。 放僻邪侈。乃得贫贱之道。舍去旧习。自当不至贫贱。而如其节俭勤谨而反至于贫贱。则只可安分。不可求去。俗读不以其道。两处异吐。窃恐皆当作어든若作라도吐则是谓放僻邪侈而得贫贱。亦不可去也。溪门质疑以为大谬。苟有异义。则朱子于此。当别下虽字矣。盖道德仁义。而得富贵。君子固当处也。放僻邪侈而得贫贱。亦当去也。攀缘蹊径而得富贵。君子固不处也。水火盗贼而得贫贱。亦不去也。
不以其道两处。未见异吐。惟上下得之异吐。而此盖为君子而设语者也。放僻邪侈。固是得贫贱之道。然焉有君子而为放僻邪侈。至于贫贱耶。此则在所不论。如勉斋所谓水火盗贼。诖误陷刑等事。君子亦或有所不免。而此其不以道得之者也。不以道得之。则宜若可去。而慕富贵而恶贫贱者。小人之所为也。审富贵而安贫贱者。君子之所为也。所以于富贵。则不处其不当得之富贵。于贫贱则不去其不当得之贫贱。而不去与不处。意实相反。其吐不得不异也。
无适无莫章。 君子之于动静云为之间。有所适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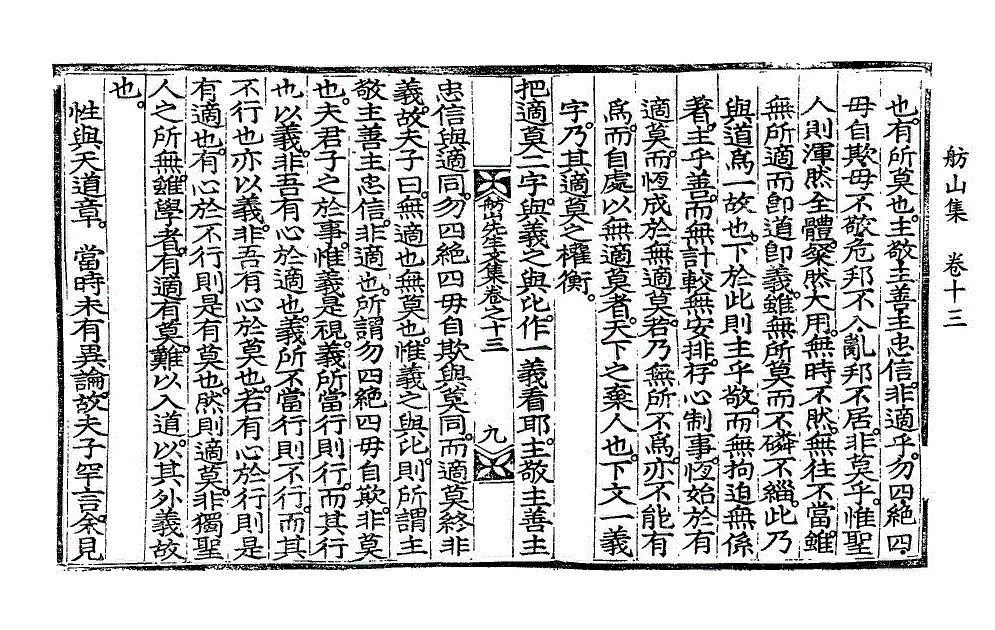 也。有所莫也。主敬,主善,主忠信。非适乎。勿四,绝四,毋自欺,毋不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非莫乎。惟圣人则浑然全体。粲然大用。无时不然。无往不当。虽无所适而即道即义。虽无所莫而不磷不缁。此乃与道为一故也。下于此则主乎敬。而无拘迫无系著。主乎善。而无计较无安排。存心制事。恒始于有适莫。而恒成于无适莫。若乃无所不为。亦不能有为。而自处以无适莫者。天下之弃人也。下文一义字。乃其适莫之权衡。
也。有所莫也。主敬,主善,主忠信。非适乎。勿四,绝四,毋自欺,毋不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非莫乎。惟圣人则浑然全体。粲然大用。无时不然。无往不当。虽无所适而即道即义。虽无所莫而不磷不缁。此乃与道为一故也。下于此则主乎敬。而无拘迫无系著。主乎善。而无计较无安排。存心制事。恒始于有适莫。而恒成于无适莫。若乃无所不为。亦不能有为。而自处以无适莫者。天下之弃人也。下文一义字。乃其适莫之权衡。把适莫二字。与义之与比。作一义看耶。主敬主善主忠信与适同。勿四绝四毋自欺与莫同。而适莫终非义。故夫子曰。无适也无莫也。惟义之与比。则所谓主敬主善主忠信。非适也。所谓勿四绝四毋自欺。非莫也。夫君子之于事。惟义是视。义所当行则行。而其行也以义。非吾有心于适也。义所不当行则不行。而其不行也亦以义。非吾有心于莫也。若有心于行则是有适也。有心于不行则是有莫也。然则适莫。非独圣人之所无。虽学者。有适有莫。难以入道。以其外义故也。
性与天道章。 当时未有异论。故夫子罕言。余见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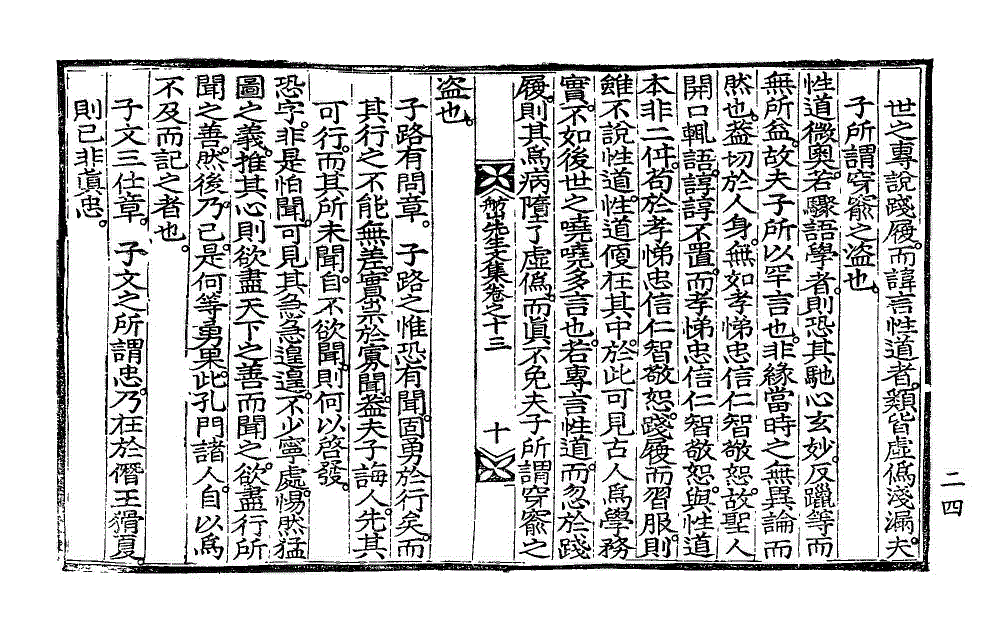 世之专说践履。而讳言性道者。类皆虚伪浅漏。夫子所谓穿窬之盗也。
世之专说践履。而讳言性道者。类皆虚伪浅漏。夫子所谓穿窬之盗也。性道微奥。若骤语学者。则恐其驰心玄妙。反躐等而无所益。故夫子所以罕言也。非缘当时之无异论而然也。盖切于人身。无如孝悌忠信仁智敬恕。故圣人开口辄语。谆谆不置。而孝悌忠信仁智敬恕。与性道本非二件。苟于孝悌忠信仁智敬恕。践履而习服。则虽不说性道。性道便在其中。于此可见古人为学务实。不如后世之哓哓多言也。若专言性道。而忽于践履。则其为病堕了虚伪。而真不免夫子所谓穿窬之盗也。
子路有问章。 子路之惟恐有闻。固勇于行矣。而其行之不能无差。实祟于寡闻。盖夫子诲人。先其可行。而其所未闻。自不欲闻。则何以启发。
恐字。非是怕闻。可见其急急遑遑。不少宁处。惕然猛图之义。推其心则欲尽天下之善而闻之。欲尽行所闻之善。然后。乃已。是何等勇果。此孔门诸人。自以为不及而记之者也。
子文三仕章。 子文之所谓忠。乃在于僭王猾夏。则已非真忠。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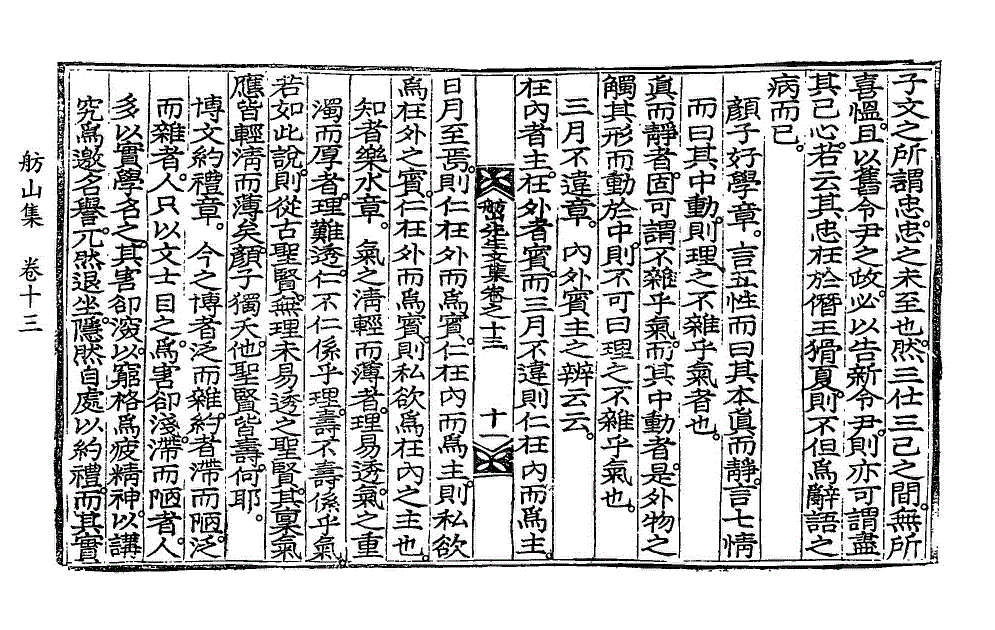 子文之所谓忠。忠之未至也。然三仕三已之间。无所喜愠。且以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则亦可谓尽其己心。若云其忠在于僭王猾夏。则不但为辞语之病而已。
子文之所谓忠。忠之未至也。然三仕三已之间。无所喜愠。且以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则亦可谓尽其己心。若云其忠在于僭王猾夏。则不但为辞语之病而已。颜子好学章。 言五性而曰其本真而静。言七情而曰其中动。则理之不杂乎气者也。
真而静者。固可谓不杂乎气。而其中动者。是外物之触其形而动于中。则不可曰理之不杂乎气也。
三月不违章。 内外宾主之辨云云。
在内者主。在外者宾。而三月不违则仁在内而为主。日月至焉。则仁在外而为宾。仁在内而为主。则私欲为在外之宾。仁在外而为宾。则私欲为在内之主也。
知者乐水章。 气之清轻而薄者。理易透。气之重浊而厚者。理难透。仁不仁系乎理。寿不寿系乎气。
若如此说。则从古圣贤。无理未易透之圣贤。其禀气应皆轻清而薄矣。颜子独夭。他圣贤皆寿。何耶。
博文约礼章。 今之博者泛而杂。约者滞而陋。泛而杂者。人只以文士目之。为害却浅。滞而陋者。人多以实学名之。其害却深。以穷格为疲精神。以讲究为邀名誉。兀然退坐。隐然自处以约礼。而其实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L 页
 则阴为不善。反甚于向所谓杂者。
则阴为不善。反甚于向所谓杂者。俗流之弊虽如此。而以此足(去声)此章之旨。还似泛而不切。
子见南子章。 天厌之矢。似有愤激之意。想必子路刚强。语侵宫壸。将至于不佳之景色。故夫子发此誓。
此论与饶氏说相似。然圣人岂为他信吾言。而故设愤激于言辞之际也。且南子之行。国人之所恶。则语侵宫壸。拖出不佳之景色云者。殊不衬当。如集注说。然后方是称停。
用行舍藏章。 以势言则藏固易。行固难。以道言则藏为重。行为轻。又曰。行之尤难。
既云藏为重。复云行尤难。未可晓耳。
求仁得仁章。 辄苟非当立之人。则子路之刚。视公山,南子。若唾洟然。况仕于无父国乎。
辄之不当立。据夫子之言可知也。子路之终仕于卫。以及于祸。是子路之见义不明也。岂以子路仕之之故。而谓辄以当立乎。
发愤忘食章。 愤与乐。在得道与否。则皆发于义理之正者也。或以此亦属气发之情误矣。(愤至于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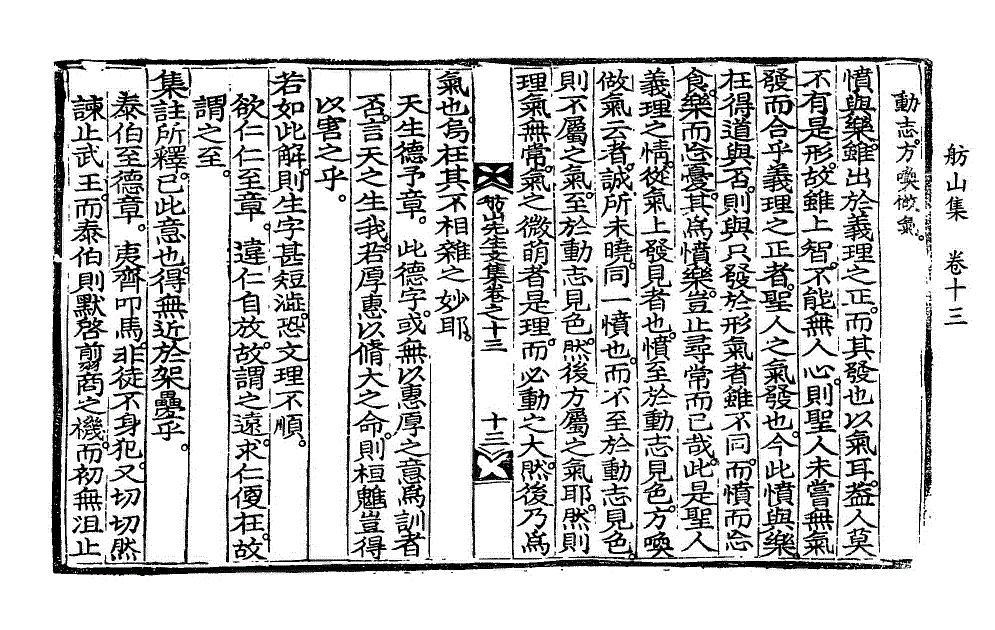 动志。方唤做气。)
动志。方唤做气。)愤与乐。虽出于义理之正。而其发也以气耳。盖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则圣人未尝无气发而合乎义理之正者。圣人之气发也。今此愤与乐。在得道与否。则与只发于形气者虽不同。而愤而忘食。乐而忘忧。其为愤乐。岂止寻常而已哉。此是圣人义理之情。从气上发见者也。愤至于动志见色。方唤做气云者。诚所未晓。同一愤也。而不至于动志见色。则不属之气。至于动志见色。然后方属之气耶。然则理气无常。气之微萌者是理。而必动之大。然后乃为气也。乌在其不相杂之妙耶。
天生德予章。 此德字。或无以惠厚之意为训者否。言天之生我。若厚惠以脩大之命。则桓魋岂得以害之乎。
若如此解。则生字甚短涩。恐文理不顺。
欲仁仁至章。 违仁自放。故谓之远。求仁便在。故谓之至。
集注所释。已此意也。得无近于架叠乎。
泰伯至德章。 夷齐叩马。非徒不身犯。又切切然谏止武王。而泰伯则默启剪商之机。而初无沮止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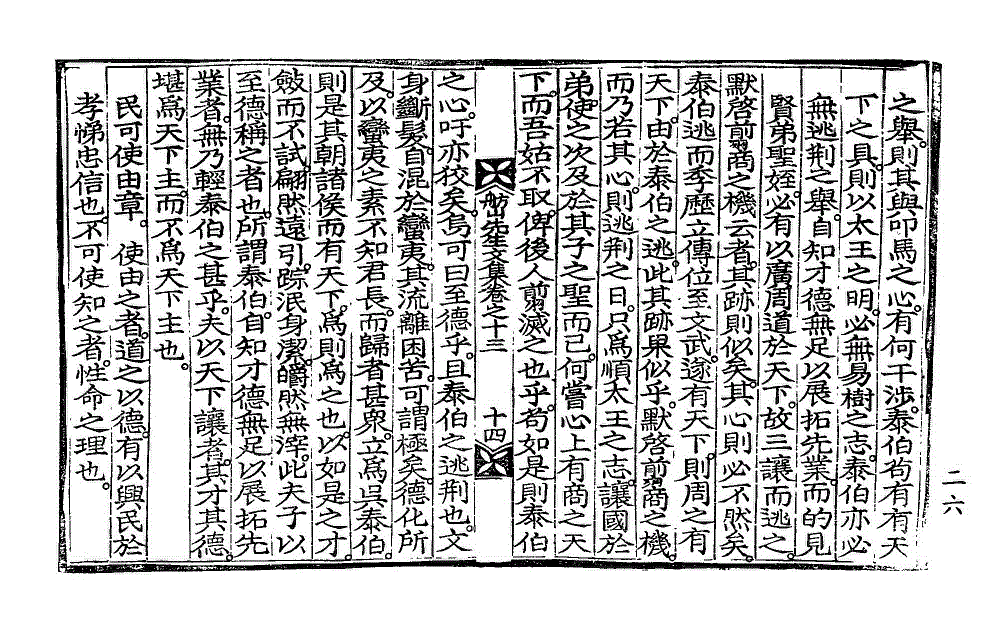 之举。则其与叩马之心。有何干涉。泰伯苟有有天下之具。则以太王之明。必无易树之志。泰伯亦必无逃荆之举。自知才德无足以展拓先业。而的见贤弟圣侄。必有以广周道于天下。故三让而逃之。
之举。则其与叩马之心。有何干涉。泰伯苟有有天下之具。则以太王之明。必无易树之志。泰伯亦必无逃荆之举。自知才德无足以展拓先业。而的见贤弟圣侄。必有以广周道于天下。故三让而逃之。默启剪商之机云者。其迹则似矣。其心则必不然矣。泰伯逃而季历立传位至文武。遂有天下。则周之有天下。由于泰伯之逃。此其迹果似乎。默启剪商之机。而乃若其心。则逃荆之日。只为顺太王之志。让国于弟。使之次及于其子之圣而已。何尝心上有商之天下。而吾姑不取。俾后人剪灭之也乎。苟如是则泰伯之心。吁亦狡矣。乌可曰至德乎。且泰伯之逃荆也。文身断发。自混于蛮夷。其流离困苦。可谓极矣。德化所及。以蛮夷之素不知君长。而归者甚众。立为吴泰伯。则是其朝诸侯而有天下。为则为之也。以如是之才。敛而不试。翩然远引。踪泯身洁。皭然无滓。此夫子以至德称之者也。所谓泰伯。自知才德无足以展拓先业者。无乃轻泰伯之甚乎。夫以天下让者。其才其德。堪为天下主。而不为天下主也。
民可使由章。 使由之者。道之以德。有以兴民于孝悌忠信也。不可使知之者。性命之理也。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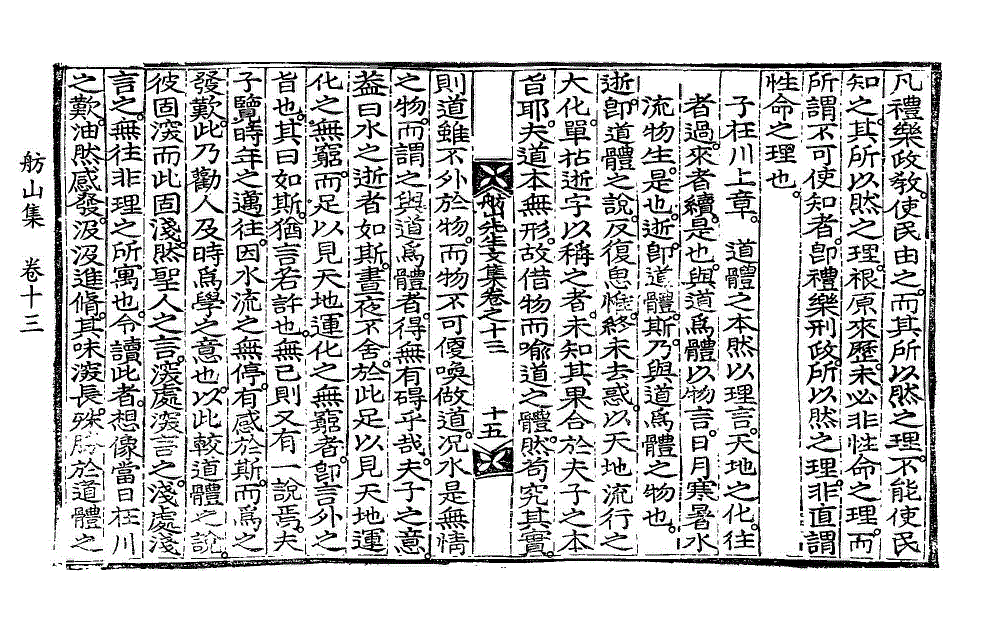 凡礼乐政教。使民由之。而其所以然之理。不能使民知之。其所以然之理。根原来历。未必非性命之理。而所谓不可使知者。即礼乐刑政。所以然之理。非直谓性命之理也。
凡礼乐政教。使民由之。而其所以然之理。不能使民知之。其所以然之理。根原来历。未必非性命之理。而所谓不可使知者。即礼乐刑政。所以然之理。非直谓性命之理也。子在川上章。 道体之本然以理言。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是也。与道为体以物言。日月寒暑水流物生。是也。逝。即道体。斯。乃与道为体之物也。
逝。即道体之说。反复思惟。终未去惑。以天地流行之大化。单拈逝字以称之者。未知其果合于夫子之本旨耶。夫道本无形。故借物而喻道之体。然苟究其实。则道虽不外于物。而物不可便唤做道。况水是无情之物。而谓之与道为体者。得无有碍乎哉。夫子之意。盖曰水之逝者如斯。昼夜不舍。于此足以见天地运化之无穷。而足以见天地运化之无穷者。即言外之旨也。其曰如斯。犹言若许也。无已则又有一说焉。夫子览时年之迈往。因水流之无停。有感于斯。而为之发叹。此乃劝人及时为学之意也。以此较道体之说。彼固深而此固浅。然圣人之言。深处深言之。浅处浅言之。无往非理之所寓也。令读此者。想像当日在川之叹。油然感发。汲汲进脩。其味深长。殊胜于道体之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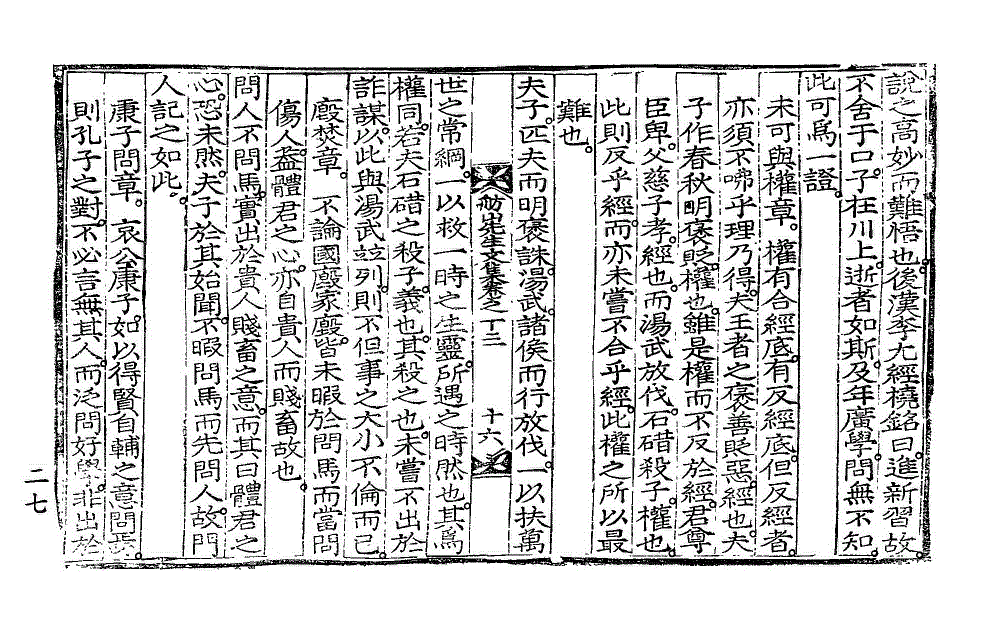 说之高妙而难悟也。后汉李尤经桡铭曰。进新习故。不舍于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广学。问无不知。此可为一證。
说之高妙而难悟也。后汉李尤经桡铭曰。进新习故。不舍于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广学。问无不知。此可为一證。未可与权章。 权有合经底。有反经底。但反经者。亦须不咈乎理乃得。夫王者之褒善贬恶。经也。夫子作春秋明褒贬。权也。虽是权而不反于经。君尊臣卑。父慈子孝。经也。而汤武放伐。石碏杀子。权也。此则反乎经。而亦未尝不合乎经。此权之所以最难也。
夫子。匹夫而明褒诛。汤武。诸侯而行放伐。一以扶万世之常纲。一以救一时之生灵。所遇之时然也。其为权同。若夫石碏之杀子。义也。其杀之也。未尝不出于诈谋。以此与汤武并列。则不但事之大小不伦而已。
厩焚章。 不论国厩家厩。皆未暇于问马而当问伤人。盖体君之心。亦自贵人而贱畜故也。
问人不问马。实出于贵人贱畜之意。而其曰体君之心。恐未然。夫子于其始闻。不暇问马而先问人。故门人记之如此。
康子问章。 哀公,康子。如以得贤自辅之意问焉。则孔子之对。不必言无其人。而泛问好学。非出于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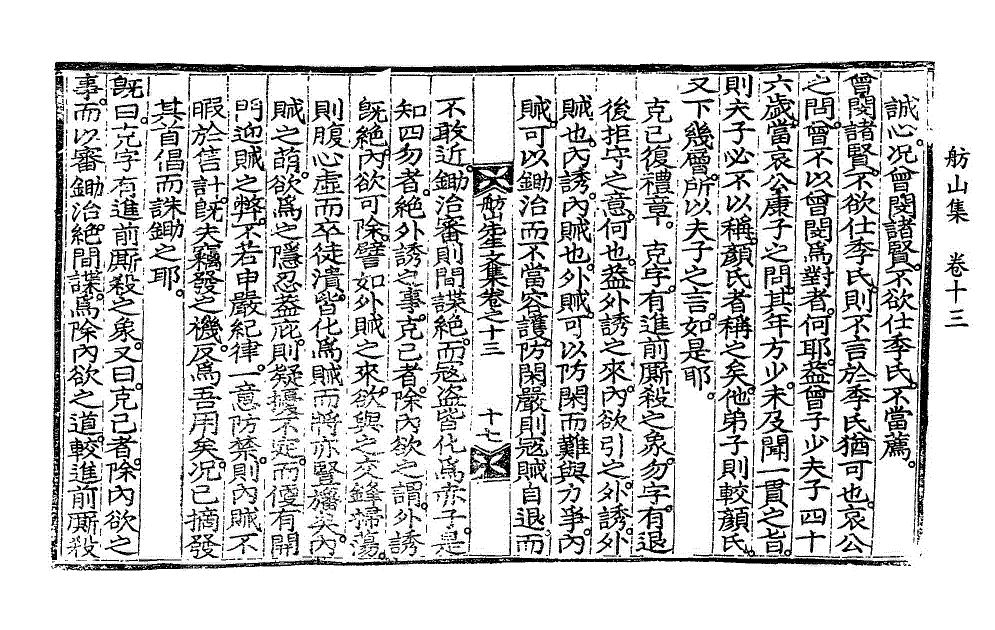 诚心。况曾,闵诸贤。不欲仕季氏。不当荐。
诚心。况曾,闵诸贤。不欲仕季氏。不当荐。曾,闵诸贤。不欲仕季氏。则不言于季氏犹可也。哀公之问。曾不以曾闵为对者。何耶。盖曾子少夫子四十六岁。当哀公,康子之问。其年方少。未及闻一贯之旨。则夫子必不以称。颜氏者称之矣。他弟子则较颜氏。又下几层。所以夫子之言。如是耶。
克己复礼章。 克字。有进前厮杀之象。勿字。有退后拒守之意。何也。盖外诱之来。内欲引之。外诱。外贼也。内诱。内贼也。外贼。可以防闲而难与力争。内贼。可以锄治而不当容护。防闲严则寇贼自退。而不敢近。锄治审则间谍绝。而寇盗皆化为赤子。是知四勿者。绝外诱之事。克己者。除内欲之谓。外诱既绝。内欲可除。譬如外贼之来。欲与之交锋扫荡。则腹心虚而卒徒溃。皆化为贼而将亦竖幡矣。内贼之萌。欲为之隐忍盖庇。则疑扰不定。而便有开门迎贼之弊。不若申严纪律。一意防禁。则内贼不暇于售计。既失窃发之机。反为吾用矣。况已摘发其首倡而诛锄之耶。
既曰。克字有进前厮杀之象。又曰。克己者。除内欲之事。而以审锄治。绝间谍。为除内欲之道。较进前厮杀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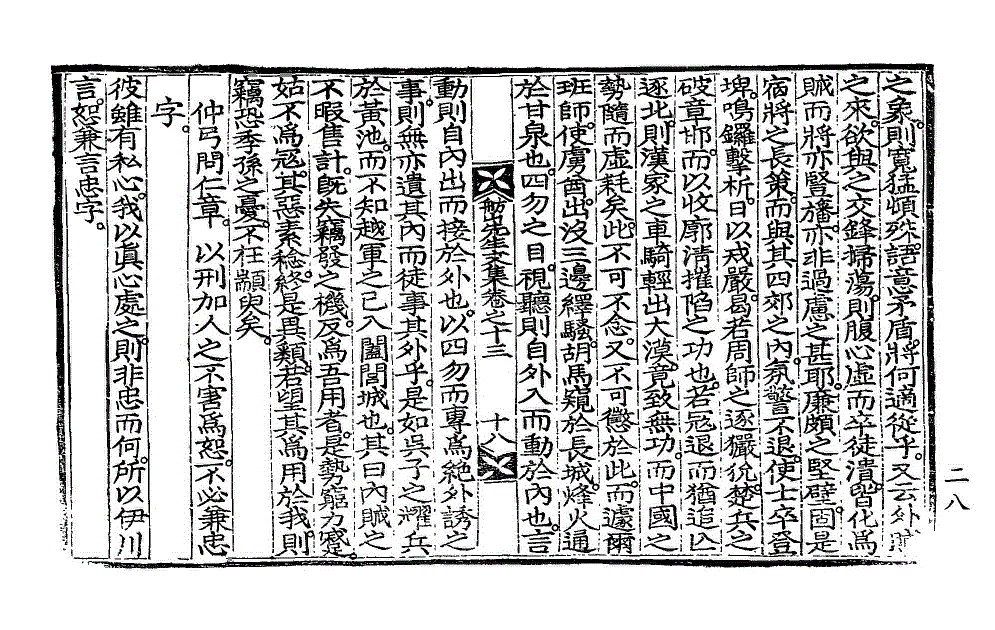 之象。则宽猛顿殊。语意矛盾。将何适从乎。又云外贼之来。欲与之交锋扫荡。则腹心虚而卒徒溃。皆化为贼而将亦竖幡。亦非过虑之甚耶。廉颇之坚壁。固是宿将之长策。而与其四郊之内。氛警不退。使士卒登埤。鸣锣击柝。日以戒严。曷若周师之逐猃狁。楚兵之破章邯。而以收廓清摧陷之功也。若寇退而犹追亡逐北。则汉家之车骑轻出大漠。竟致无功。而中国之势随而虚耗矣。此不可不念。又不可惩于此。而遽尔班师。使虏酋。出没三边绎骚。胡马窥于长城。烽火通于甘泉也。四勿之目。视听则自外入而动于内也。言动则自内出而接于外也。以四勿而专为绝外诱之事。则无亦遗其内而徒事其外乎。是如吴子之耀兵于黄池。而不知越军之已入阖闾城也。其曰内贼之不暇售计。既失窃发之机。反为吾用者。是势穷力蹙。姑不为寇。其恶素稔。终是异类。若望其为用于我。则窃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矣。
之象。则宽猛顿殊。语意矛盾。将何适从乎。又云外贼之来。欲与之交锋扫荡。则腹心虚而卒徒溃。皆化为贼而将亦竖幡。亦非过虑之甚耶。廉颇之坚壁。固是宿将之长策。而与其四郊之内。氛警不退。使士卒登埤。鸣锣击柝。日以戒严。曷若周师之逐猃狁。楚兵之破章邯。而以收廓清摧陷之功也。若寇退而犹追亡逐北。则汉家之车骑轻出大漠。竟致无功。而中国之势随而虚耗矣。此不可不念。又不可惩于此。而遽尔班师。使虏酋。出没三边绎骚。胡马窥于长城。烽火通于甘泉也。四勿之目。视听则自外入而动于内也。言动则自内出而接于外也。以四勿而专为绝外诱之事。则无亦遗其内而徒事其外乎。是如吴子之耀兵于黄池。而不知越军之已入阖闾城也。其曰内贼之不暇售计。既失窃发之机。反为吾用者。是势穷力蹙。姑不为寇。其恶素稔。终是异类。若望其为用于我。则窃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矣。仲弓问仁章。 以刑加人之不害为恕。不必兼忠字。
彼虽有私心。我以真心处之。则非忠而何。所以伊川言。恕兼言忠字。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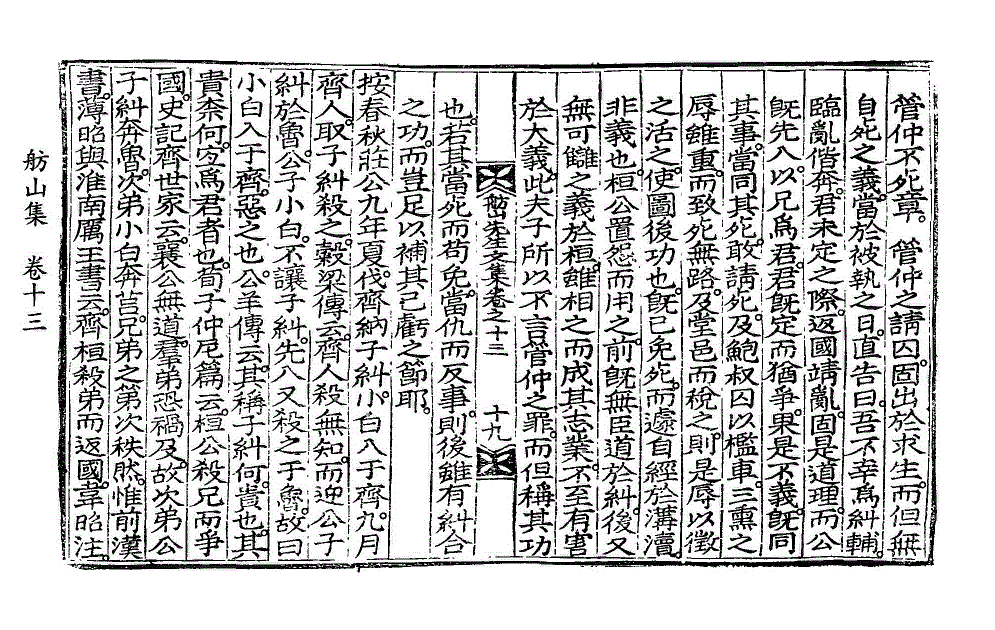 管仲不死章。 管仲之请囚。固出于求生。而但无自死之义。当于被执之日。直告曰。吾不幸为纠辅。临乱偕奔。君未定之际。返国靖乱。固是道理。而公既先入。以兄为君。君既定而犹争。果是不义。既同其事。当同其死。敢请死。及鲍叔囚以槛车。三熏之辱虽重。而致死无路。及堂邑而税之。则是辱以徵之活之。使图后功也。既已免死。而遽自经于沟渎。非义也。桓公置怨而用之。前既无臣道于纠。后又无可雠之义于桓。虽相之而成其志业。不至有害于大义。此夫子所以不言管仲之罪。而但称其功也。若其当死而苟免。当仇而反事。则后虽有纠合之功。而岂足以补其已亏之节耶。
管仲不死章。 管仲之请囚。固出于求生。而但无自死之义。当于被执之日。直告曰。吾不幸为纠辅。临乱偕奔。君未定之际。返国靖乱。固是道理。而公既先入。以兄为君。君既定而犹争。果是不义。既同其事。当同其死。敢请死。及鲍叔囚以槛车。三熏之辱虽重。而致死无路。及堂邑而税之。则是辱以徵之活之。使图后功也。既已免死。而遽自经于沟渎。非义也。桓公置怨而用之。前既无臣道于纠。后又无可雠之义于桓。虽相之而成其志业。不至有害于大义。此夫子所以不言管仲之罪。而但称其功也。若其当死而苟免。当仇而反事。则后虽有纠合之功。而岂足以补其已亏之节耶。按春秋庄公九年夏。伐齐纳子纠。小白入于齐。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谷梁传云。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故曰小白入于齐。恶之也。公羊传云。其称子纠何。贵也。其贵柰何。宜为君者也。荀子仲尼篇云。桓公杀兄而争国。史记齐世家云。襄公无道。群弟恐祸及。故次弟公子纠奔鲁。次弟小白奔莒。兄弟之第次秩然。惟前汉书。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齐桓杀弟而返国。韦昭注。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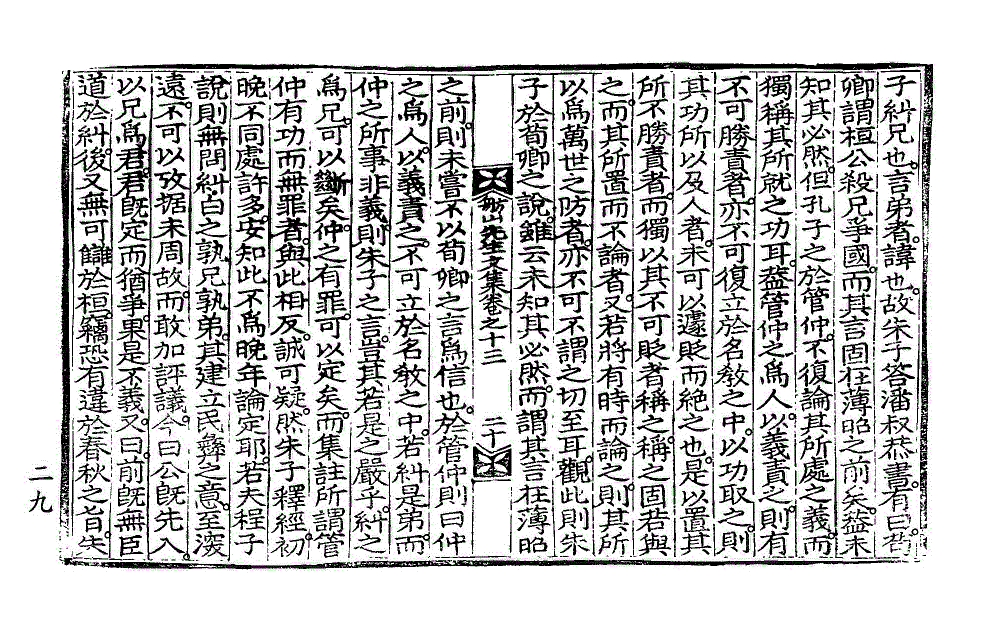 子纠兄也。言弟者。讳也。故朱子答潘叔恭书。有曰。苟卿谓桓公杀兄争国。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盖未知其必然。但孔子之于管仲。不复论其所处之义。而独称其所就之功耳。盖管仲之为人。以义责之。则有不可胜责者。亦不可复立于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则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贬而绝之也。是以置其所不胜责者。而独以其不可贬者称之。称之固若与之。而其所置而不论者。又若将有时而论之。则其所以为万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谓之切至耳。观此则朱子于荀卿之说。虽云未知其必然。而谓其言在薄昭之前。则未尝不以荀卿之言为信也。于管仲则曰仲之为人。以义责之。不可立于名教之中。若纠是弟。而仲之所事非义。则朱子之言。岂其若是之严乎。纠之为兄。可以断矣。仲之有罪。可以定矣。而集注所谓管仲有功而无罪者。与此相反。诚可疑。然朱子释经。初晚不同处许多。安知此不为晚年论定耶。若夫程子说则无问纠,白之孰兄孰弟。其建立民彝之意。至深远。不可以考据未周故。而敢加评议。今曰公既先入。以兄为君。君既定而犹争。果是不义。又曰。前既无臣道于纠。后又无可雠于桓。窃恐有违于春秋之旨。朱
子纠兄也。言弟者。讳也。故朱子答潘叔恭书。有曰。苟卿谓桓公杀兄争国。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盖未知其必然。但孔子之于管仲。不复论其所处之义。而独称其所就之功耳。盖管仲之为人。以义责之。则有不可胜责者。亦不可复立于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则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贬而绝之也。是以置其所不胜责者。而独以其不可贬者称之。称之固若与之。而其所置而不论者。又若将有时而论之。则其所以为万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谓之切至耳。观此则朱子于荀卿之说。虽云未知其必然。而谓其言在薄昭之前。则未尝不以荀卿之言为信也。于管仲则曰仲之为人。以义责之。不可立于名教之中。若纠是弟。而仲之所事非义。则朱子之言。岂其若是之严乎。纠之为兄。可以断矣。仲之有罪。可以定矣。而集注所谓管仲有功而无罪者。与此相反。诚可疑。然朱子释经。初晚不同处许多。安知此不为晚年论定耶。若夫程子说则无问纠,白之孰兄孰弟。其建立民彝之意。至深远。不可以考据未周故。而敢加评议。今曰公既先入。以兄为君。君既定而犹争。果是不义。又曰。前既无臣道于纠。后又无可雠于桓。窃恐有违于春秋之旨。朱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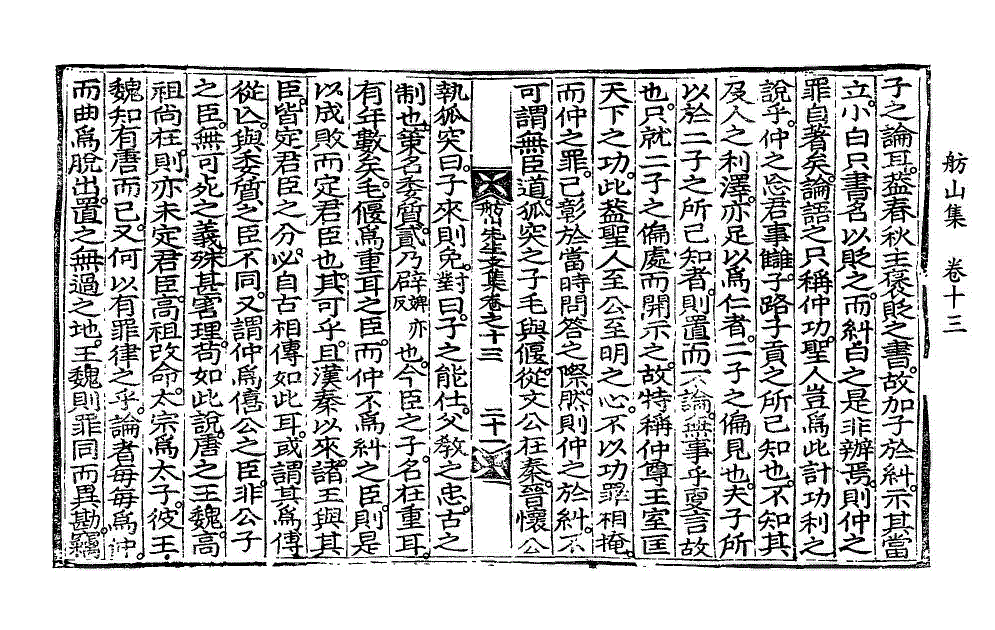 子之论耳。盖春秋主褒贬之书。故加子于纠。示其当立。小白只书名以贬之。而纠,白之是非办焉。则仲之罪自著矣。论语之只称仲功。圣人岂为此计功利之说乎。仲之忘君事雠。子路,子贡之所已知也。不知其及人之利泽。亦足以为仁者。二子之偏见也。夫子所以于二子之所已知者。则置而不论。无事乎更言故也。只就二子之偏处而开示之。故特称仲尊王室匡天下之功。此盖圣人至公至明之心。不以功罪相掩。而仲之罪。已彰于当时问答之际。然则仲之于纠。不可谓无臣道。狐突之子毛与偃。从文公在秦。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婢亦反)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不为纠之臣。则是以成败而定君臣也。其可乎。且汉秦以来。诸王与其臣。皆定君臣之分。必自古相传如此耳。或谓其为傅从亡。与委质之臣不同。又谓仲为僖公之臣。非公子之臣。无可死之义。殊甚害理。苟如此说。唐之王,魏。高祖尚在。则亦未定君臣。高祖改命。太宗为太子。彼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论者每每为仲。而曲为脱出。置之无过之地。王,魏则罪同而异勘。窃
子之论耳。盖春秋主褒贬之书。故加子于纠。示其当立。小白只书名以贬之。而纠,白之是非办焉。则仲之罪自著矣。论语之只称仲功。圣人岂为此计功利之说乎。仲之忘君事雠。子路,子贡之所已知也。不知其及人之利泽。亦足以为仁者。二子之偏见也。夫子所以于二子之所已知者。则置而不论。无事乎更言故也。只就二子之偏处而开示之。故特称仲尊王室匡天下之功。此盖圣人至公至明之心。不以功罪相掩。而仲之罪。已彰于当时问答之际。然则仲之于纠。不可谓无臣道。狐突之子毛与偃。从文公在秦。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婢亦反)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不为纠之臣。则是以成败而定君臣也。其可乎。且汉秦以来。诸王与其臣。皆定君臣之分。必自古相传如此耳。或谓其为傅从亡。与委质之臣不同。又谓仲为僖公之臣。非公子之臣。无可死之义。殊甚害理。苟如此说。唐之王,魏。高祖尚在。则亦未定君臣。高祖改命。太宗为太子。彼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论者每每为仲。而曲为脱出。置之无过之地。王,魏则罪同而异勘。窃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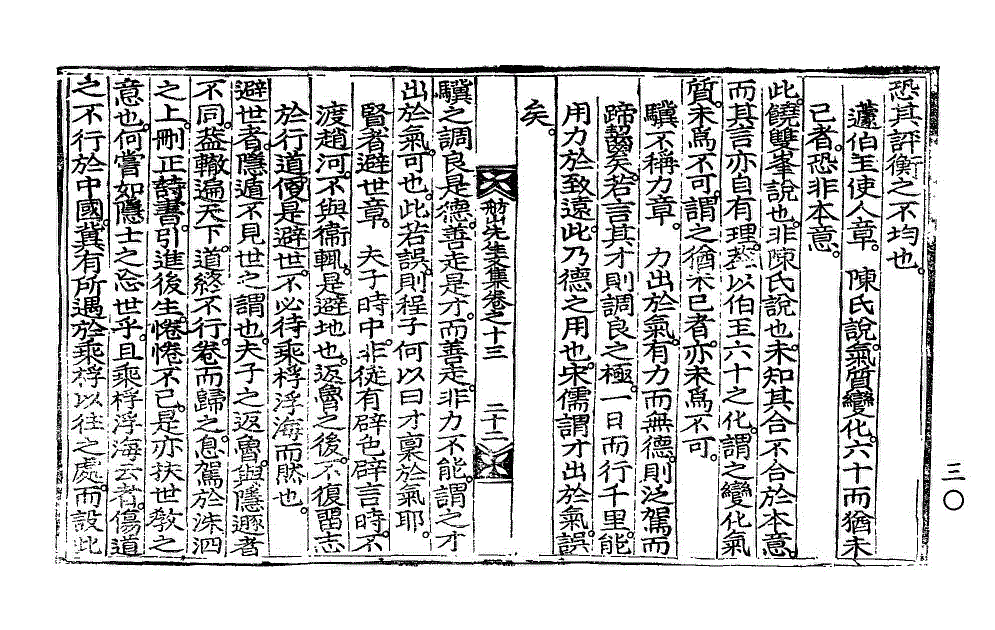 恐其评衡之不均也。
恐其评衡之不均也。蘧伯玉使人章。 陈氏说。气质变化。六十而犹未已者。恐非本意。
此。饶双峰说也。非陈氏说也。未知其合不合于本意。而其言亦自有理。盖以伯玉六十之化。谓之变化气质。未为不可。谓之犹未已者。亦未为不可。
骥不称力章。 力出于气。有力而无德。则泛驾而蹄齧矣。若言其才则调良之极。一日而行千里。能用力于致远。此乃德之用也。宋儒谓才出于气。误矣。
骥之调良是德。善走是才。而善走。非力不能。谓之才出于气。可也。此若误。则程子何以曰才禀于气耶。
贤者避世章。 夫子时中。非徒有辟色辟言时。不渡赵河。不与卫辄。是避地也。返鲁之后。不复留志于行道。便是避世。不必待乘桴浮海而然也。
避世者。隐遁不见世之谓也。夫子之返鲁。与隐遁者不同。盖辙遍天下。道终不行。卷而归之。息驾于洙泗之上。删正诗书。引进后生。惓惓不已。是亦扶世教之意也。何尝如隐士之忘世乎。且乘桴浮海云者。伤道之不行于中国。冀有所遇于乘桴以往之处。而设此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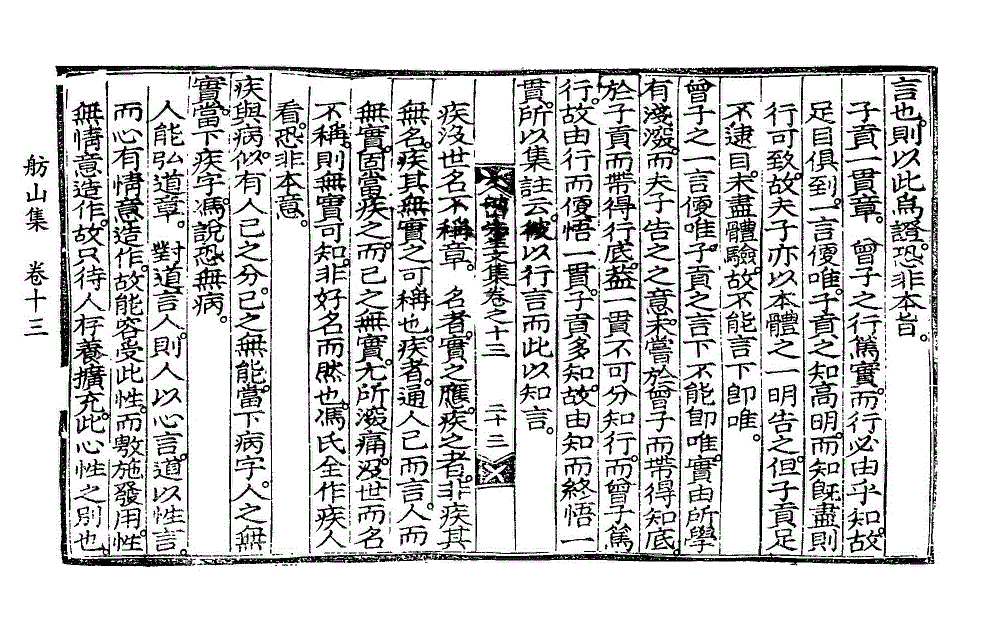 言也。则以此为證。恐非本旨。
言也。则以此为證。恐非本旨。子贡一贯章。 曾子之行笃实。而行必由乎知。故足目俱到。一言便唯。子贡之知高明。而知既尽则行可致。故夫子亦以本体之一明告之。但子贡足不逮目。未尽体验。故不能言下即唯。
曾子之一言便唯。子贡之言下不能即唯。实由所学有浅深。而夫子告之之意。未尝于曾子而带得知底。于子贡而带得行底。盖一贯不可分知行。而曾子笃行。故由行而便悟一贯。子贡多知。故由知而终悟一贯。所以集注云。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
疾没世名不称章。 名者。实之应。疾之者。非疾其无名。疾其无实之可称也。疾者。通人己而言。人而无实。固当疾之。而己之无实。尤所深痛。没世而名不称。则无实可知。非好名而然也。冯氏全作疾人看。恐非本意。
疾与病。似有人己之分。己之无能。当下病字。人之无实。当下疾字。冯说恐无病。
人能弘道章。 对道言人。则人以心言。道以性言。而心有情意造作。故能容受此性。而敷施发用。性无情意造作。故只待人存养扩充。此心性之别也。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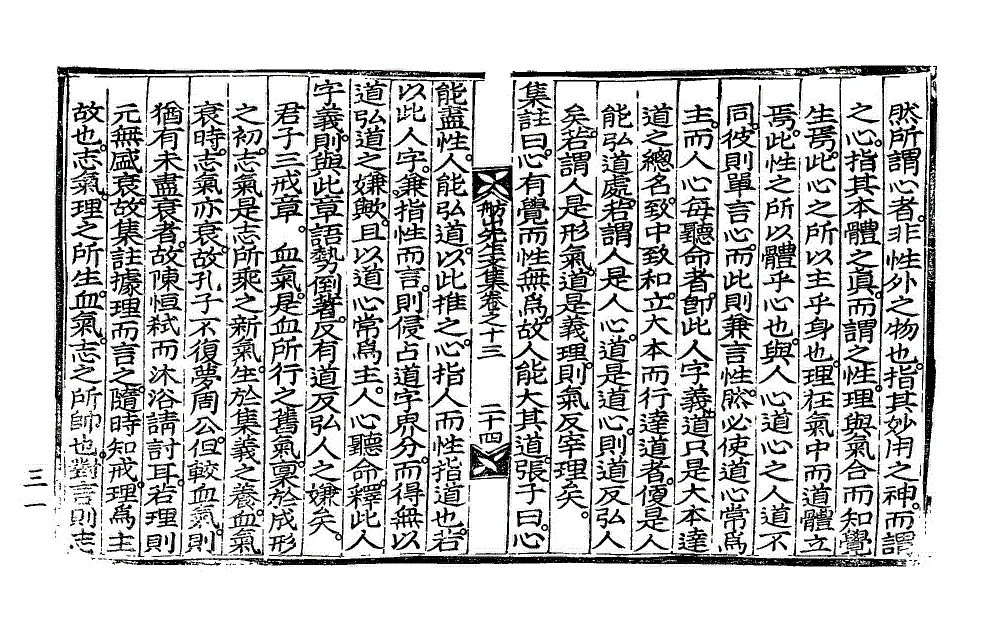 然所谓心者。非性外之物也。指其妙用之神。而谓之心。指其本体之真。而谓之性。理与气合而知觉生焉。此心之所以主乎身也。理在气中而道体立焉。此性之所以体乎心也。与人心道心之人道不同。彼则单言心。而此则兼言性。然必使道心常为主。而人心每听命者。即此人字义。道只是大本达道之总名。致中致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便是人能弘道处。若谓人是人心。道是道心。则道反弘人矣。若谓人是形气。道是义理。则气反宰理矣。
然所谓心者。非性外之物也。指其妙用之神。而谓之心。指其本体之真。而谓之性。理与气合而知觉生焉。此心之所以主乎身也。理在气中而道体立焉。此性之所以体乎心也。与人心道心之人道不同。彼则单言心。而此则兼言性。然必使道心常为主。而人心每听命者。即此人字义。道只是大本达道之总名。致中致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便是人能弘道处。若谓人是人心。道是道心。则道反弘人矣。若谓人是形气。道是义理。则气反宰理矣。集注曰。心有觉而性无为。故人能大其道。张子曰。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以此推之。心指人而性指道也。若以此人字。兼指性而言。则侵占道字界分。而得无以道弘道之嫌欤。且以道心常为主。人心听命。释此人字义。则与此章语势倒著。反有道反弘人之嫌矣。
君子三戒章。 血气。是血所行之旧气。禀于成形之初。志气是志所乘之新气。生于集义之养。血气衰时。志气亦衰。故孔子不复梦周公。但较血气。则犹有未尽衰者。故陈恒弑而沐浴请讨耳。若理则元无盛衰。故集注据理而言之。随时知戒。理为主故也。志气。理之所生。血气。志之所帅也。对言则志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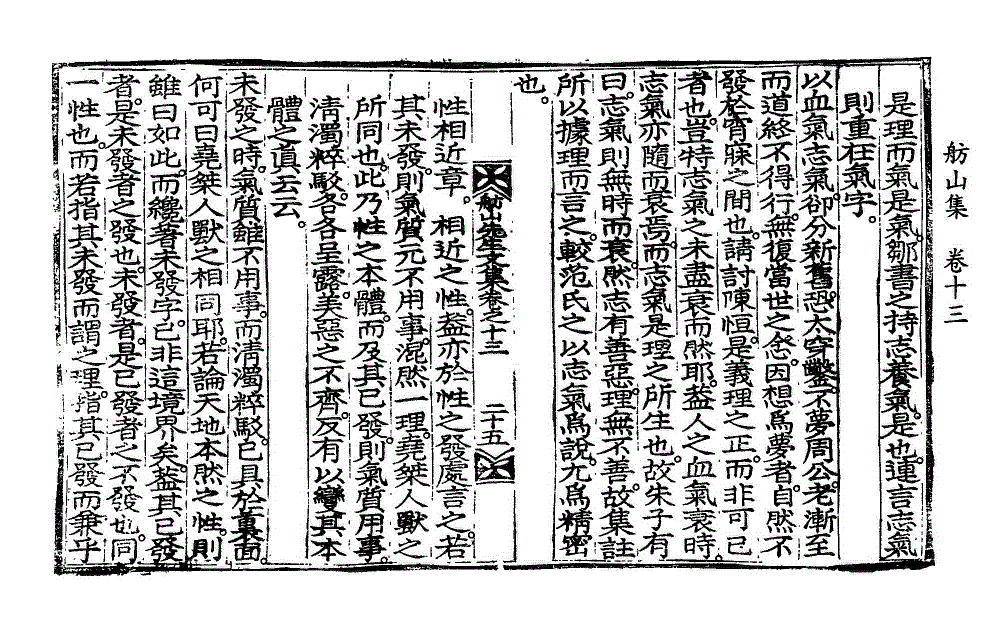 是理而气是气。邹书之持志养气。是也。连言志气则重在气字。
是理而气是气。邹书之持志养气。是也。连言志气则重在气字。以血气志气。却分新旧。恐太穿凿。不梦周公。老渐至而道终不得行。无复当世之念。因想为梦者。自然不发于宵寐之间也。请讨陈恒。是义理之正。而非可已者也。岂特志气之未尽衰而然耶。盖人之血气衰时。志气亦随而衰焉。而志气是理之所生也。故朱子有曰。志气则无时而衰。然志有善恶。理无不善。故集注所以据理而言之。较范氏之以志气为说。尤为精密也。
性相近章。 相近之性。盖亦于性之发处言之。若其未发。则气质元不用事。混然一理。尧桀人兽之所同也。此乃性之本体。而及其已发。则气质用事。清浊粹驳。各各呈露。美恶之不齐。反有以变其本体之真云云。
未发之时。气质虽不用事。而清浊粹驳。已具于里面。何可曰尧桀人兽之相同耶。若论天地本然之性。则虽曰如此。而才著未发字。已非这境界矣。盖其已发者。是未发者之发也。未发者。是已发者之不发也。同一性也。而若指其未发而谓之理。指其已发而兼乎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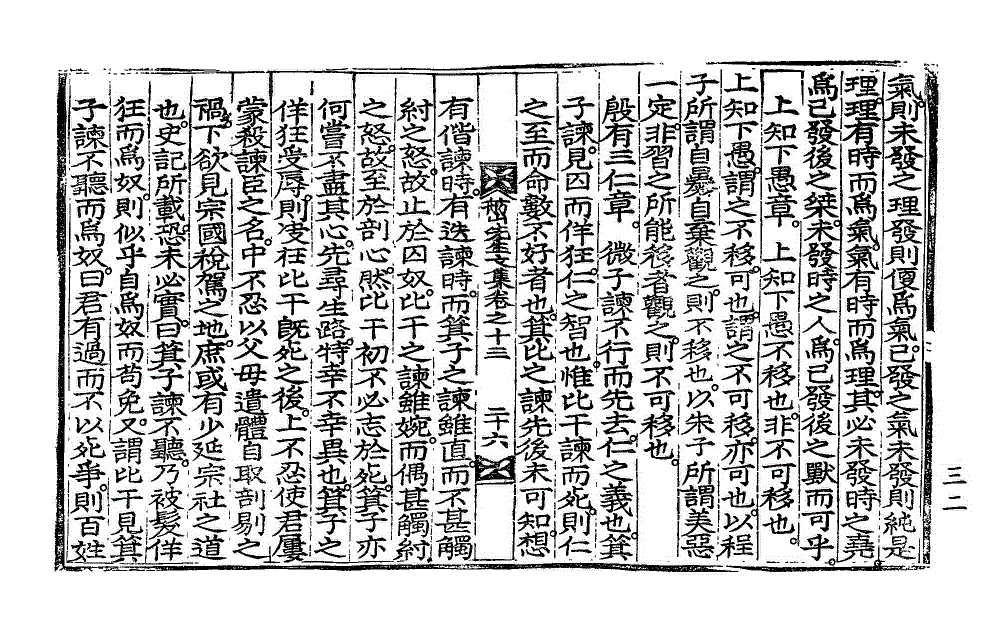 气。则未发之理发则便为气。已发之气未发则纯是理。理有时而为气。气有时而为理。其必未发时之尧。为已发后之桀。未发时之人。为已发后之兽而可乎。
气。则未发之理发则便为气。已发之气未发则纯是理。理有时而为气。气有时而为理。其必未发时之尧。为已发后之桀。未发时之人。为已发后之兽而可乎。上知下愚章。 上知下愚不移也。非不可移也。
上知下愚。谓之不移。可也。谓之不可移。亦可也。以程子所谓自㬥自弃观之。则不移也。以朱子所谓美恶一定。非习之所能移者观之。则不可移也。
殷有三仁章。 微子谏不行而先去。仁之义也。箕子谏。见囚而佯狂。仁之智也。惟比干谏而死。则仁之至而命数不好者也。箕,比之谏先后未可知。想有偕谏时。有迭谏时。而箕子之谏虽直。而不甚触纣之怒。故止于囚奴。比干之谏虽婉。而偶甚触纣之怒。故至于剖心。然比干初不必志于死。箕子亦何尝不尽其心。先寻生路。特幸不幸异也。箕子之佯狂受辱。则决在比干既死之后。上不忍使君屡蒙杀谏臣之名。中不忍以父母遗体自取剖剔之祸。下欲见宗国税驾之地。庶或有少延宗社之道也。史记所载。恐未必实。曰箕子谏不听。乃被发佯狂而为奴。则似乎自为奴而苟免。又谓比干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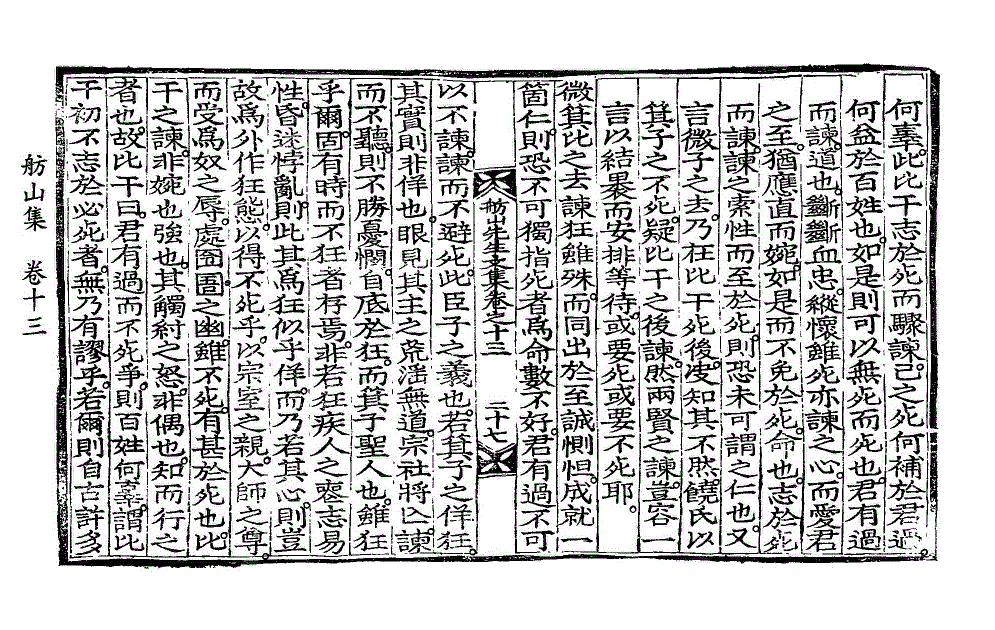 何辜。此比干志于死而骤谏。己之死何补于君过。何益于百姓也。如是则可以无死而死也。君有过而谏。道也。断断血忠。纵怀虽死亦谏之心。而爱君之至。犹应直而婉。如是而不免于死。命也。志于死而谏。谏之索性而至于死。则恐未可谓之仁也。又言微子之去。乃在比干死后。决知其不然。饶氏以箕子之不死。疑比干之后谏。然两贤之谏。岂容一言以结裹而安排等待。或要死或要不死耶。
何辜。此比干志于死而骤谏。己之死何补于君过。何益于百姓也。如是则可以无死而死也。君有过而谏。道也。断断血忠。纵怀虽死亦谏之心。而爱君之至。犹应直而婉。如是而不免于死。命也。志于死而谏。谏之索性而至于死。则恐未可谓之仁也。又言微子之去。乃在比干死后。决知其不然。饶氏以箕子之不死。疑比干之后谏。然两贤之谏。岂容一言以结裹而安排等待。或要死或要不死耶。微箕比之去谏狂虽殊。而同出于至诚恻怛。成就一个仁。则恐不可独指死者为命数不好。君有过不可以不谏。谏而不避死。此臣子之义也。若箕子之佯狂。其实则非佯也。眼见其主之荒淫无道。宗社将亡。谏而不听。则不胜忧悯。自底于狂。而箕子圣人也。虽狂乎尔。固有时而不狂者存焉。非若狂疾人之丧志易性。昏迷悖乱。则此其为狂似乎佯。而乃若其心。则岂故为外作狂态。以得不死乎。以宗室之亲。大师之尊。而受为奴之辱。处囹圄之幽。虽不死。有甚于死也。比干之谏。非婉也强也。其触纣之怒。非偶也。知而行之者也。故比干曰。君有过而不死争。则百姓何辜。谓比干初不志于必死者。无乃有谬乎。若尔则自古许多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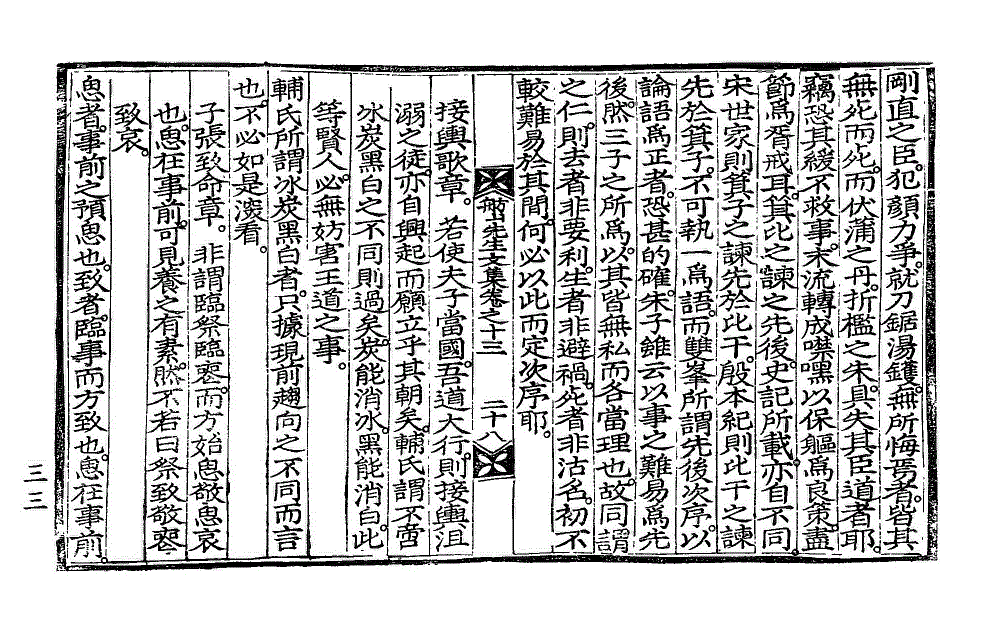 刚直之臣。犯颜力争。就刀锯汤镬。无所悔焉者。皆其无死而死。而伏蒲之丹。折槛之朱。具失其臣道者耶。窃恐其缓不救事。末流转成噤嘿以保躯为良策。尽节为胥戒耳。箕比之谏之先后。史记所载。亦自不同。宋世家则箕子之谏先于比干。殷本纪则比干之谏先于箕子。不可执一为语。而双峰所谓先后次序。以论语为正者。恐甚的确。朱子虽云以事之难易为先后。然三子之所为。以其皆无私而各当理也。故同谓之仁。则去者非要利。生者非避祸。死者非沽名。初不较难易于其间。何必以此而定次序耶。
刚直之臣。犯颜力争。就刀锯汤镬。无所悔焉者。皆其无死而死。而伏蒲之丹。折槛之朱。具失其臣道者耶。窃恐其缓不救事。末流转成噤嘿以保躯为良策。尽节为胥戒耳。箕比之谏之先后。史记所载。亦自不同。宋世家则箕子之谏先于比干。殷本纪则比干之谏先于箕子。不可执一为语。而双峰所谓先后次序。以论语为正者。恐甚的确。朱子虽云以事之难易为先后。然三子之所为。以其皆无私而各当理也。故同谓之仁。则去者非要利。生者非避祸。死者非沽名。初不较难易于其间。何必以此而定次序耶。接舆歌章。 若使夫子当国。吾道大行。则接舆沮溺之徒。亦自兴起而愿立乎其朝矣。辅氏谓不啻冰炭黑白之不同则过矣。炭能消冰。黑能消白。此等贤人。必无妨害王道之事。
辅氏所谓冰炭黑白者。只据现前趋向之不同而言也。不必如是深看。
子张致命章。 非谓临祭临丧。而方始思敬思哀也。思在事前。可见养之有素。然不若曰祭致敬丧致哀。
思者。事前之预思也。致者。临事而方致也。思在事前。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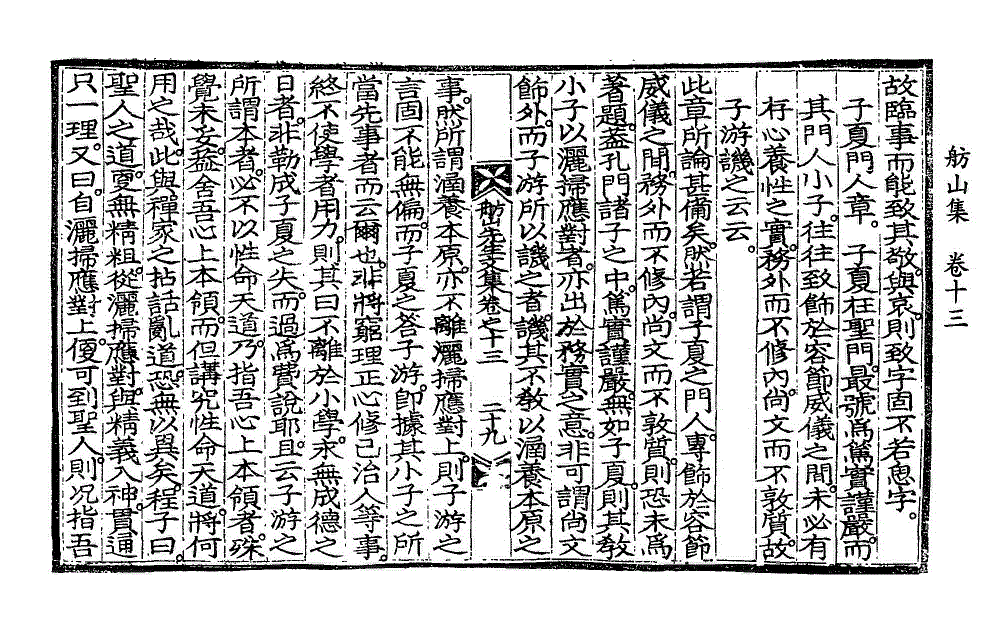 故临事而能致其敬。与哀。则致字固不若思字。
故临事而能致其敬。与哀。则致字固不若思字。子夏门人章。 子夏在圣门。最号为笃实谨严。而其门人小子。往往致饰于容节威仪之间。未必有存心养性之实。务外而不修内。尚文而不敦质。故子游讥之云云。
此章所论甚备矣。然若谓子夏之门人。专饰于容节威仪之间。务外而不修内。尚文而不敦质。则恐未为著题。盖孔门诸子之中。笃实谨严。无如子夏。则其教小子以洒扫应对者。亦出于务实之意。非可谓尚文饰外。而子游所以讥之者。讥其不教以涵养本原之事。然所谓涵养本原。亦不离洒扫应对上。则子游之言固不能无偏。而子夏之答子游。即据其小子之所当先事者而云尔也。非将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等事。终不使学者用力。则其曰不离于小学。永无成德之日者。非勒成子夏之失。而过为费说耶。且云子游之所谓本者。必不以性命天道。乃指吾心上本领者。殊觉未妥。盖舍吾心上本领。而但讲究性命天道。将何用之哉。此与禅家之拈话乱道。恐无以异矣。程子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则况指吾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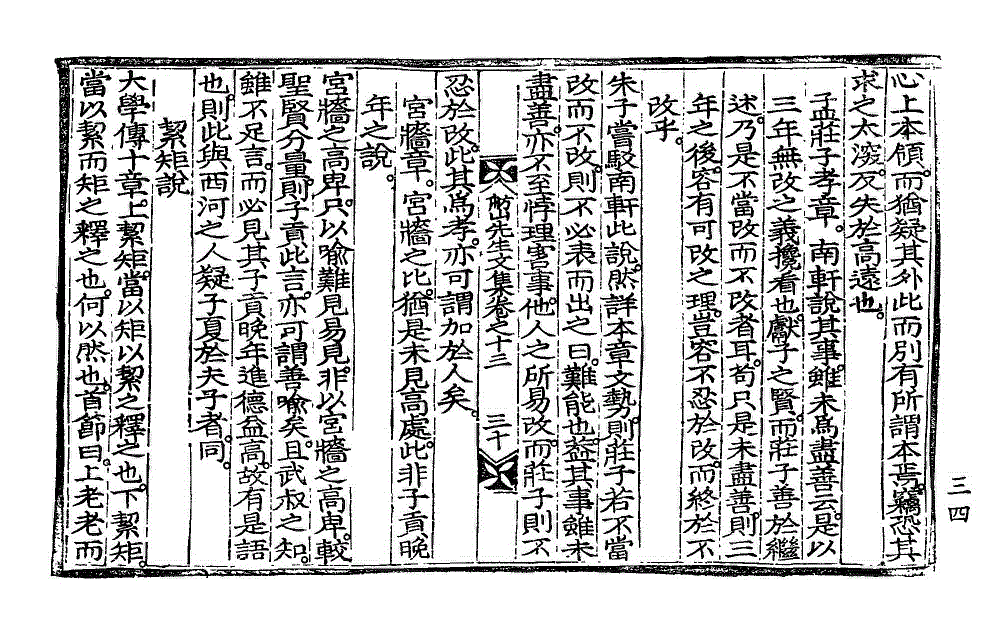 心上本领。而犹疑其外此而别有所谓本焉。窃恐其求之太深。反失于高远也。
心上本领。而犹疑其外此而别有所谓本焉。窃恐其求之太深。反失于高远也。孟庄子孝章。 南轩说其事。虽未为尽善云。是以三年无改之义搀看也。献子之贤。而庄子善于继述。乃是不当改而不改者耳。苟只是未尽善。则三年之后。容有可改之理。岂容不忍于改。而终于不改乎。
朱子尝驳南轩此说。然详本章文势。则庄子若不当改而不改。则不必表而出之曰。难能也。盖其事虽未尽善。亦不至悖理害事。他人之所易改。而庄子则不忍于改。此其为孝。亦可谓加于人矣。
宫墙章。 宫墙之比。犹是未见高处。此非子贡晚年之说。
宫墙之高卑。只以喻难见易见。非以宫墙之高卑。较圣贤分量。则子贡此言。亦可谓善喻矣。且武叔之知。虽不足言。而必见其子贡晚年进德益高。故有是语也。则此与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者。同。
絜矩说
大学传十章。上絜矩。当以矩以絜之释之也。下絜矩。当以絜而矩之释之也。何以然也。首节曰。上老老而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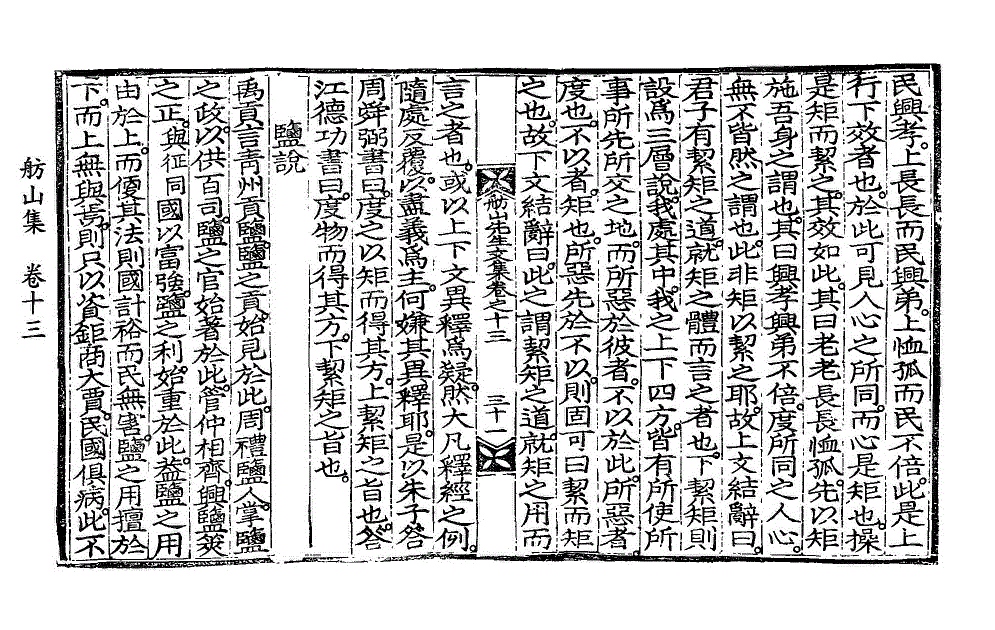 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此是上行下效者也。于此可见人心之所同。而心是矩也。操是矩而絜之。其效如此。其曰老老长长恤孤。先以矩施吾身之谓也。其曰兴孝兴弟不倍。度所同之人心。无不皆然之谓也。此非矩以絜之耶。故上文结辞曰。君子有絜矩之道。就矩之体而言之者也。下絜矩则设为三层说。我处其中。我之上下四方。皆有所使所事所先所交之地。而所恶于彼者。不以于此。所恶者。度也。不以者。矩也。所恶先于不以。则固可曰絜而矩之也。故下文结辞曰。此之谓絜矩之道。就矩之用而言之者也。或以上下文异释为疑。然大凡释经之例。随处反覆。以尽义为主。何嫌其异释耶。是以朱子答周舜弼书曰。度之以矩而得其方。上絜矩之旨也。答江德功书曰。度物而得其方。下絜矩之旨也。
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此是上行下效者也。于此可见人心之所同。而心是矩也。操是矩而絜之。其效如此。其曰老老长长恤孤。先以矩施吾身之谓也。其曰兴孝兴弟不倍。度所同之人心。无不皆然之谓也。此非矩以絜之耶。故上文结辞曰。君子有絜矩之道。就矩之体而言之者也。下絜矩则设为三层说。我处其中。我之上下四方。皆有所使所事所先所交之地。而所恶于彼者。不以于此。所恶者。度也。不以者。矩也。所恶先于不以。则固可曰絜而矩之也。故下文结辞曰。此之谓絜矩之道。就矩之用而言之者也。或以上下文异释为疑。然大凡释经之例。随处反覆。以尽义为主。何嫌其异释耶。是以朱子答周舜弼书曰。度之以矩而得其方。上絜矩之旨也。答江德功书曰。度物而得其方。下絜矩之旨也。盐说
禹贡言青州贡盐。盐之贡。始见于此。周礼盐人。掌盐之政。以供百司。盐之官始著于此。管仲相齐。兴盐筴之正。(与征同)国以富强。盐之利。始重于此。盖盐之用由于上。而便其法则国计裕而民无害。盐之用擅于下。而上无与焉。则只以资钜商大贾。民国俱病。此不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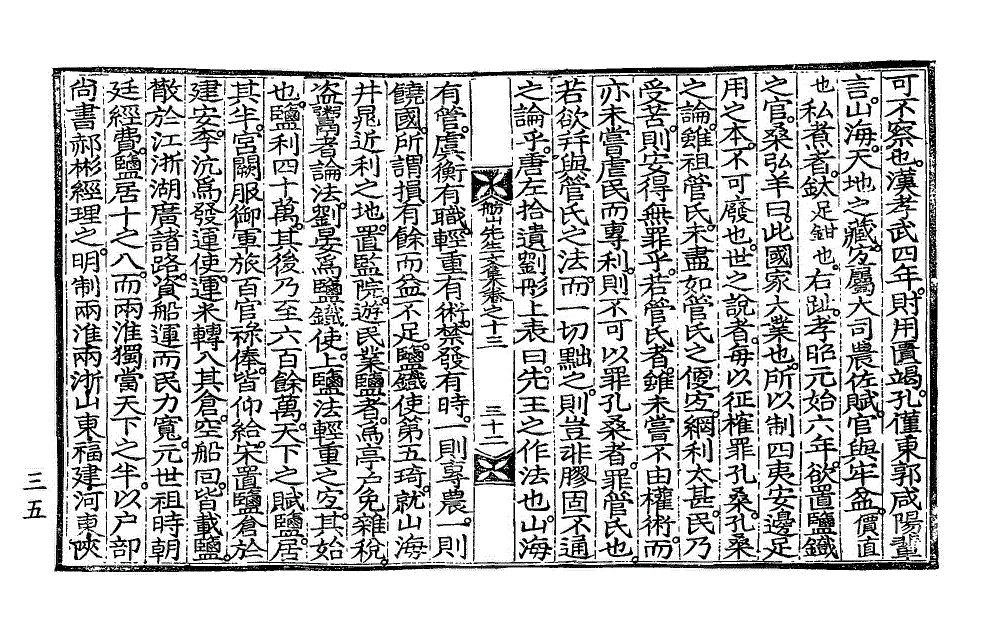 可不察也。汉孝武四年。财用匮竭。孔仅,东郭咸阳辈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大司农佐赋。官与牢盆。(价直也)私煮者。钛(足钳也。)右趾。孝昭元始六年。欲置盐铁之官。桑弘羊曰。此国家大业也。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世之说者。每以征榷罪孔桑。孔桑之论。虽祖管氏。未尽如管氏之便宜。网利太甚。民乃受苦。则安得无罪乎。若管氏者。虽未尝不由权术。而亦未尝虐民而专利。则不可以罪孔桑者。罪管氏也。若欲并与管氏之法。而一切黜之。则岂非胶固不通之论乎。唐左拾遗刘彤上表曰。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管。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一则饶国。所谓损有馀而益不足。盐铁使第五琦。就山海井晁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税。盗鬻者论法。刘晏为盐铁使。上盐法轻重之宜。其始也。盐利四十万。其后乃至六百馀万。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宫阙服御军旅百官禄俸。皆仰给。宋置盐仓于建安。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资船运而民力宽。元世祖时朝廷经费。盐居十之八。而两淮独当天下之半。以户部尚书郝彬经理之。明制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东,陕
可不察也。汉孝武四年。财用匮竭。孔仅,东郭咸阳辈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大司农佐赋。官与牢盆。(价直也)私煮者。钛(足钳也。)右趾。孝昭元始六年。欲置盐铁之官。桑弘羊曰。此国家大业也。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世之说者。每以征榷罪孔桑。孔桑之论。虽祖管氏。未尽如管氏之便宜。网利太甚。民乃受苦。则安得无罪乎。若管氏者。虽未尝不由权术。而亦未尝虐民而专利。则不可以罪孔桑者。罪管氏也。若欲并与管氏之法。而一切黜之。则岂非胶固不通之论乎。唐左拾遗刘彤上表曰。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管。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一则饶国。所谓损有馀而益不足。盐铁使第五琦。就山海井晁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税。盗鬻者论法。刘晏为盐铁使。上盐法轻重之宜。其始也。盐利四十万。其后乃至六百馀万。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宫阙服御军旅百官禄俸。皆仰给。宋置盐仓于建安。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资船运而民力宽。元世祖时朝廷经费。盐居十之八。而两淮独当天下之半。以户部尚书郝彬经理之。明制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东,陕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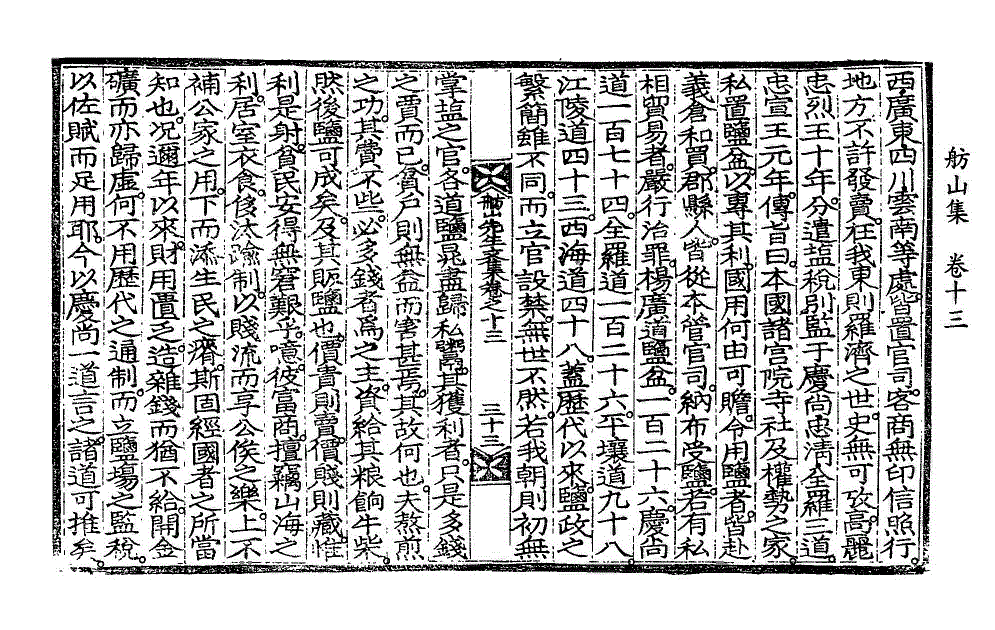 西,广东,四川,云南等处。皆置官司。客商无印信照行。地方不许发卖。在我东则罗济之世。史无可考。高丽忠烈王十年。分遣盐税别监于庆尚,忠清,全罗三道。忠宣王元年。传旨曰。本国诸宫院寺社及权势之家。私置盐盆。以专其利。国用何由可赡。令用盐者。皆赴义仓和买。郡县人。皆从本管官司。纳布受盐。若有私相贸易者。严行治罪。杨广道盐盆。一百二十六。庆尚道一百七十四。全罗道一百二十六。平壤道九十八。江陵道四十三。西海道四十八。盖历代以来。盐政之繁简虽不同。而立官设禁。无世不然。若我朝则初无掌盐之官。各道盐晁尽归私鬻。其获利者。只是多钱之贾而已。贫户则无益而害甚焉。其故何也。夫熬煎之功。其费不些。必多钱者为之主。资给其粮饷牛柴。然后盐可成矣。及其贩盐也。价贵则卖。价贱则藏。惟利是射。贫民安得无窘艰乎。噫。彼富商。擅窃山海之利。居室衣食。侈汰踰制。以贱流而享公侯之乐。上不补公家之用。下而添生民之瘠。斯固经国者之所当知也。况迩年以来。财用匮乏。造杂钱而犹不给。开金矿而亦归虚。何不用历代之通制。而立盐场之监税。以佐赋而足用耶。今以庆尚一道言之。诸道可推矣。
西,广东,四川,云南等处。皆置官司。客商无印信照行。地方不许发卖。在我东则罗济之世。史无可考。高丽忠烈王十年。分遣盐税别监于庆尚,忠清,全罗三道。忠宣王元年。传旨曰。本国诸宫院寺社及权势之家。私置盐盆。以专其利。国用何由可赡。令用盐者。皆赴义仓和买。郡县人。皆从本管官司。纳布受盐。若有私相贸易者。严行治罪。杨广道盐盆。一百二十六。庆尚道一百七十四。全罗道一百二十六。平壤道九十八。江陵道四十三。西海道四十八。盖历代以来。盐政之繁简虽不同。而立官设禁。无世不然。若我朝则初无掌盐之官。各道盐晁尽归私鬻。其获利者。只是多钱之贾而已。贫户则无益而害甚焉。其故何也。夫熬煎之功。其费不些。必多钱者为之主。资给其粮饷牛柴。然后盐可成矣。及其贩盐也。价贵则卖。价贱则藏。惟利是射。贫民安得无窘艰乎。噫。彼富商。擅窃山海之利。居室衣食。侈汰踰制。以贱流而享公侯之乐。上不补公家之用。下而添生民之瘠。斯固经国者之所当知也。况迩年以来。财用匮乏。造杂钱而犹不给。开金矿而亦归虚。何不用历代之通制。而立盐场之监税。以佐赋而足用耶。今以庆尚一道言之。诸道可推矣。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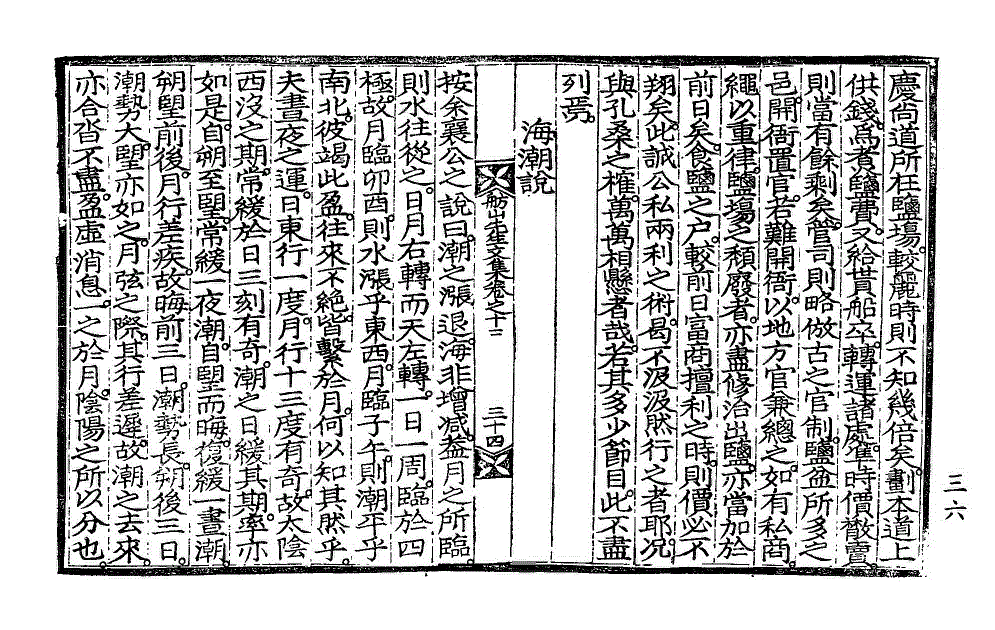 庆尚道所在盐场。较丽时则不知几倍矣。划本道上供钱。为煮盐费。又给贳船卒。转运诸处。准时价散卖。则当有馀剩矣。管司则略仿古之官制。盐盆所多之邑。开衙置官。若难开衙。以地方官兼总之。如有私商。绳以重律。盐场之颓废者。亦尽修治出盐。亦当加于前日矣。食盐之户。较前日富商擅利之时。则价必不翔矣。此诚公私两利之术。曷不汲汲然行之者耶。况与孔桑之榷。万万相悬者哉。若其多少节目。此不尽列焉。
庆尚道所在盐场。较丽时则不知几倍矣。划本道上供钱。为煮盐费。又给贳船卒。转运诸处。准时价散卖。则当有馀剩矣。管司则略仿古之官制。盐盆所多之邑。开衙置官。若难开衙。以地方官兼总之。如有私商。绳以重律。盐场之颓废者。亦尽修治出盐。亦当加于前日矣。食盐之户。较前日富商擅利之时。则价必不翔矣。此诚公私两利之术。曷不汲汲然行之者耶。况与孔桑之榷。万万相悬者哉。若其多少节目。此不尽列焉。海潮说
按余襄公之说曰。潮之涨退。海非增减。盖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日月右转而天左转。一日一周。临于四极。故月临卯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来不绝。皆系于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昼夜之运。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阴西没之期。常缓于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缓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缓一夜潮。自望而晦。复缓一昼潮。朔望前后。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势长。朔后三日。潮势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际。其行差迟。故潮之去来。亦合沓不尽。盈虚消息。一之于月。阴阳之所以分也。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7H 页
 夫春夏。昼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盖春为阳中。秋为阴中。岁之有春秋。犹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极大。常在朔望之后。此又天地之常数也。朱子尝以余公之言为是。而答张敬夫书。有曰。天地之间。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故子午卯酉。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进退。以月至此位为节。韩南塘云余公说。今以海潮验之。全不应。而彼竭此盈之说。尤为无理。岂余公生于中国。未见海潮而臆度为言。故如是耶。朱子所谓潮之进退。以月至子午卯酉之位为节者。盖朔望月加卯酉而潮涨。两弦月加子午而潮缩。此若可通也。而月盈而潮涨。月亏而潮又涨。月盈亏相半。而潮缩既未见其相合也。而月至子午。阴阳之极。而潮反缩。至卯酉。阴阳之中。而潮反长。又未有其说也。若必谓潮应于月。则一岁之冬夏春秋。一月之晦朔弦望。一日之昼夜昏朝。其进退消长之运。同一机缄也。何独以月而为言哉。一岁无再冬再夏。一月无再晦再望。一日无再昼再夜。而潮之往来。一日而再进再退。一月而再消再长。此固自有机缄之不已。不必牵合于岁月日而为言也。且以天地之始言之。则先有天。次有水。次有地。天地既生。方有日月。
夫春夏。昼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盖春为阳中。秋为阴中。岁之有春秋。犹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极大。常在朔望之后。此又天地之常数也。朱子尝以余公之言为是。而答张敬夫书。有曰。天地之间。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故子午卯酉。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进退。以月至此位为节。韩南塘云余公说。今以海潮验之。全不应。而彼竭此盈之说。尤为无理。岂余公生于中国。未见海潮而臆度为言。故如是耶。朱子所谓潮之进退。以月至子午卯酉之位为节者。盖朔望月加卯酉而潮涨。两弦月加子午而潮缩。此若可通也。而月盈而潮涨。月亏而潮又涨。月盈亏相半。而潮缩既未见其相合也。而月至子午。阴阳之极。而潮反缩。至卯酉。阴阳之中。而潮反长。又未有其说也。若必谓潮应于月。则一岁之冬夏春秋。一月之晦朔弦望。一日之昼夜昏朝。其进退消长之运。同一机缄也。何独以月而为言哉。一岁无再冬再夏。一月无再晦再望。一日无再昼再夜。而潮之往来。一日而再进再退。一月而再消再长。此固自有机缄之不已。不必牵合于岁月日而为言也。且以天地之始言之。则先有天。次有水。次有地。天地既生。方有日月。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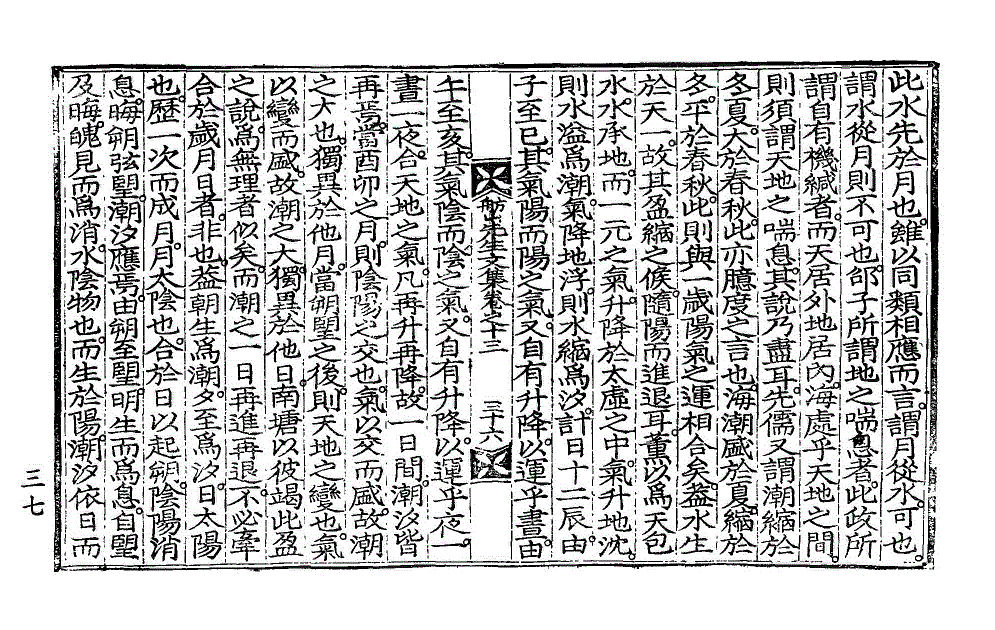 此水先于月也。虽以同类相应而言。谓月从水。可也。谓水从月则不可也。邵子所谓地之喘息者。此政所谓自有机缄者。而天居外地居内。海处乎天地之间。则须谓天地之喘息。其说乃尽耳。先儒又谓潮缩于冬夏。大于春秋。此亦臆度之言也。海潮盛于夏。缩于冬。平于春秋。此则与一岁阳气之运相合矣。盖水生于天一。故其盈缩之候。随阳而进退耳。薰以为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虚之中。气升地沈。则水溢为潮。气降地浮。则水缩为汐。计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气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一夜。合天地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间。潮汐皆再焉。当酉卯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他月。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故潮之大。独异于他日。南塘以彼竭此盈之说。为无理者似矣。而潮之一日再进再退。不必牵合于岁月日者。非也。盖朝生为潮。夕至为汐。日太阳也。历一次而成月。月太阴也。合于日以起朔。阴阳消息。晦朔弦望。潮汐应焉。由朔至望。明生而为息。自望及晦。魄见而为消。水阴物也。而生于阳。潮汐依日而
此水先于月也。虽以同类相应而言。谓月从水。可也。谓水从月则不可也。邵子所谓地之喘息者。此政所谓自有机缄者。而天居外地居内。海处乎天地之间。则须谓天地之喘息。其说乃尽耳。先儒又谓潮缩于冬夏。大于春秋。此亦臆度之言也。海潮盛于夏。缩于冬。平于春秋。此则与一岁阳气之运相合矣。盖水生于天一。故其盈缩之候。随阳而进退耳。薰以为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虚之中。气升地沈。则水溢为潮。气降地浮。则水缩为汐。计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气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一夜。合天地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间。潮汐皆再焉。当酉卯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他月。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故潮之大。独异于他日。南塘以彼竭此盈之说。为无理者似矣。而潮之一日再进再退。不必牵合于岁月日者。非也。盖朝生为潮。夕至为汐。日太阳也。历一次而成月。月太阴也。合于日以起朔。阴阳消息。晦朔弦望。潮汐应焉。由朔至望。明生而为息。自望及晦。魄见而为消。水阴物也。而生于阳。潮汐依日而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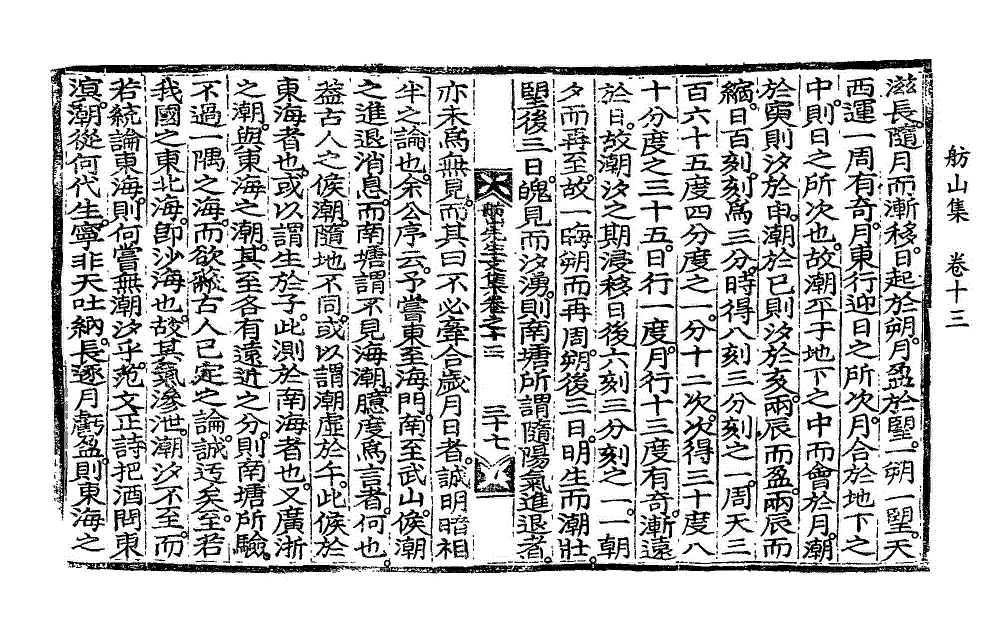 滋长。随月而渐移。日起于朔。月盈于望。一朔一望。天西运一周有奇。月东行迎日之所次。月合于地下之中。则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会于月。潮于寅则汐于申。潮于巳则汐于亥。两辰而盈。两辰而缩。日百刻。刻为三分。时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渐远于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后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后三日。明生而潮壮。望后三日。魄见而汐涌。则南塘所谓随阳气进退者。亦未为无见。而其曰不必牵合岁月日者。诚明暗相半之论也。余公序云。予尝东至海门。南至武山。候潮之进退消息。而南塘谓不见海潮。臆度为言者。何也。盖古人之候潮。随地不同。或以谓潮虚于午。此候于东海者也。或以谓生于子。此测于南海者也。又广浙之潮。与东海之潮。其至各有远近之分。则南塘所验。不过一隅之海。而欲蔽古人已定之论。诚迂矣。至若我国之东北海。即沙海也。故其气渗泄。潮汐不至。而若统论东海。则何尝无潮汐乎。范文正诗把酒问东溟。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逐月亏盈。则东海之
滋长。随月而渐移。日起于朔。月盈于望。一朔一望。天西运一周有奇。月东行迎日之所次。月合于地下之中。则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会于月。潮于寅则汐于申。潮于巳则汐于亥。两辰而盈。两辰而缩。日百刻。刻为三分。时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渐远于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后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后三日。明生而潮壮。望后三日。魄见而汐涌。则南塘所谓随阳气进退者。亦未为无见。而其曰不必牵合岁月日者。诚明暗相半之论也。余公序云。予尝东至海门。南至武山。候潮之进退消息。而南塘谓不见海潮。臆度为言者。何也。盖古人之候潮。随地不同。或以谓潮虚于午。此候于东海者也。或以谓生于子。此测于南海者也。又广浙之潮。与东海之潮。其至各有远近之分。则南塘所验。不过一隅之海。而欲蔽古人已定之论。诚迂矣。至若我国之东北海。即沙海也。故其气渗泄。潮汐不至。而若统论东海。则何尝无潮汐乎。范文正诗把酒问东溟。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逐月亏盈。则东海之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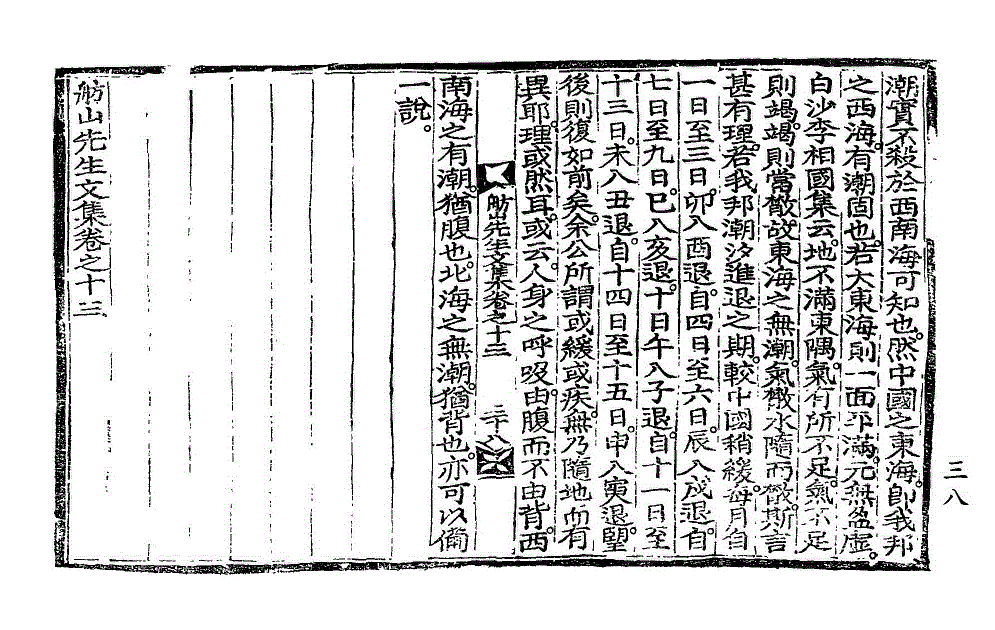 潮实不杀于西南海可知也。然中国之东海。即我邦之西海。有潮固也。若大东海则一面平满。元无盈虚。白沙李相国集云。地不满东隅。气有所不足。气不足则竭。竭则当散。故东海之无潮。气散水随而散。斯言甚有理。若我邦潮汐进退之期。较中国稍缓。每月自一日至三日。卯入酉退。自四日至六日。辰入戌退。自七日至九日。巳入亥退。十日午入子退。自十一日至十三日。未入丑退。自十四日至十五日。申入寅退。望后则复如前矣。余公所谓或缓或疾。无乃随地而有异耶。理或然耳。或云。人身之呼吸。由腹而不由背。西南海之有潮。犹腹也。北海之无潮。犹背也。亦可以备一说。
潮实不杀于西南海可知也。然中国之东海。即我邦之西海。有潮固也。若大东海则一面平满。元无盈虚。白沙李相国集云。地不满东隅。气有所不足。气不足则竭。竭则当散。故东海之无潮。气散水随而散。斯言甚有理。若我邦潮汐进退之期。较中国稍缓。每月自一日至三日。卯入酉退。自四日至六日。辰入戌退。自七日至九日。巳入亥退。十日午入子退。自十一日至十三日。未入丑退。自十四日至十五日。申入寅退。望后则复如前矣。余公所谓或缓或疾。无乃随地而有异耶。理或然耳。或云。人身之呼吸。由腹而不由背。西南海之有潮。犹腹也。北海之无潮。犹背也。亦可以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