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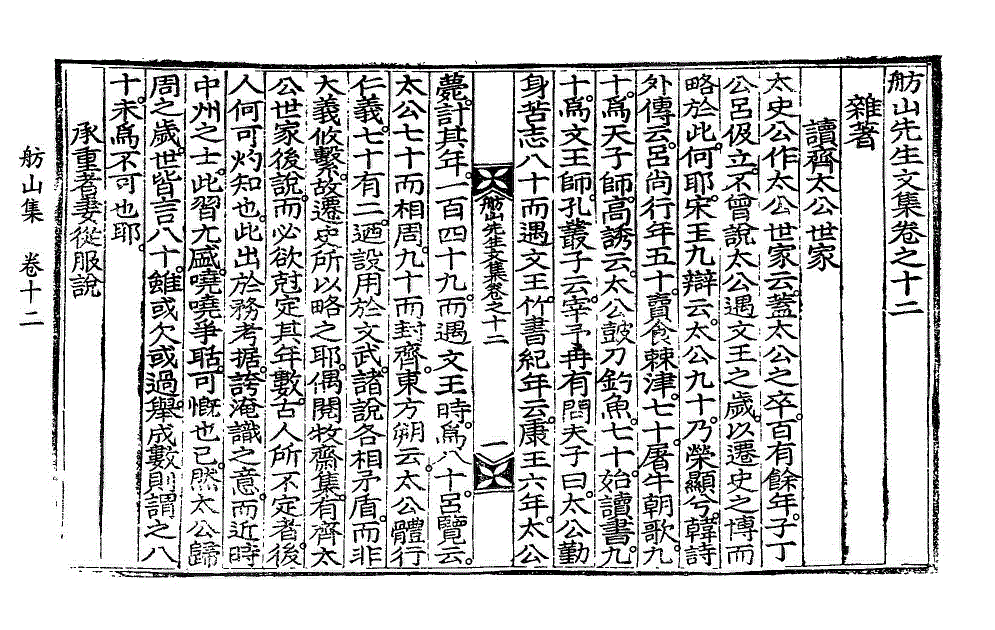 读齐太公世家
读齐太公世家太史公作太公世家云。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不曾说太公遇文王之岁。以迁史之博而略于此。何耶。宋玉九辩云。太公九十。乃荣显兮。韩诗外传云。吕尚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九十。为天子师。高诱云。太公鼓刀钓鱼。七十。始读书。九十。为文王师。孔丛子云。宰予,冉有问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竹书纪年云。康王六年。太公薨。计其年。一百四十九。而遇文王时。为八十。吕览云。太公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诸说各相矛盾。而非大义攸系。故迁史所以略之耶。偶阅牧斋集。有齐太公世家后说。而必欲尅定其年数。古人所不定者。后人何可灼知也。此出于务考据。誇淹识之意。而近时中州之士。此习尤盛。哓哓争聒。可慨也已。然太公归周之岁。世皆言八十。虽或欠或过。举成数则谓之八十。未为不可也耶。
承重者妻从服说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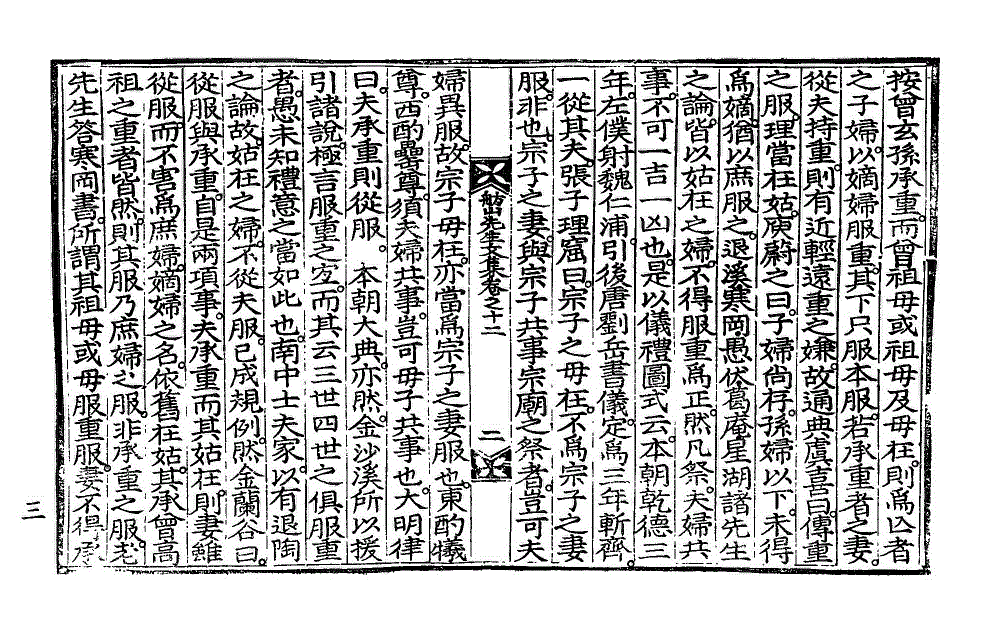 按曾玄孙承重。而曾祖母或祖母及母在。则为亡者之子妇。以嫡妇服重。其下只服本服。若承重者之妻。从夫持重。则有近轻远重之嫌。故通典虞喜曰。传重之服。理当在姑。庾蔚之曰。子妇尚存。孙妇以下。未得为嫡。犹以庶服之。退溪,寒冈,愚伏,葛庵,星湖诸先生之论。皆以姑在之妇。不得服重为正。然凡祭。夫妇共事。不可一吉一凶也。是以仪礼图式云。本朝乾德三年。左仆射魏仁浦。引后唐刘岳书仪。定为三年斩齐。一从其夫。张子理窟曰。宗子之母在。不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与宗子共事宗庙之祭者。岂可夫妇异服。故宗子母在。亦当为宗子之妻服也。东酌牺尊。西酌罍尊。须夫妇共事。岂可母子共事也。大明律曰。夫承重则从服。 本朝大典。亦然。金沙溪所以援引诸说。极言服重之宜。而其云三世四世之俱服重者。愚未知礼意之当如此也。南中士夫家。以有退陶之论故。姑在之妇。不从夫服。已成规例。然金兰谷曰。从服与承重。自是两项事。夫承重而其姑在。则妻虽从服。而不害为庶妇。嫡妇之名。依旧在姑。其承曾高祖之重者皆然。则其服乃庶妇之服。非承重之服。老先生答寒冈书。所谓其祖母或母服重服。妻不得承
按曾玄孙承重。而曾祖母或祖母及母在。则为亡者之子妇。以嫡妇服重。其下只服本服。若承重者之妻。从夫持重。则有近轻远重之嫌。故通典虞喜曰。传重之服。理当在姑。庾蔚之曰。子妇尚存。孙妇以下。未得为嫡。犹以庶服之。退溪,寒冈,愚伏,葛庵,星湖诸先生之论。皆以姑在之妇。不得服重为正。然凡祭。夫妇共事。不可一吉一凶也。是以仪礼图式云。本朝乾德三年。左仆射魏仁浦。引后唐刘岳书仪。定为三年斩齐。一从其夫。张子理窟曰。宗子之母在。不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与宗子共事宗庙之祭者。岂可夫妇异服。故宗子母在。亦当为宗子之妻服也。东酌牺尊。西酌罍尊。须夫妇共事。岂可母子共事也。大明律曰。夫承重则从服。 本朝大典。亦然。金沙溪所以援引诸说。极言服重之宜。而其云三世四世之俱服重者。愚未知礼意之当如此也。南中士夫家。以有退陶之论故。姑在之妇。不从夫服。已成规例。然金兰谷曰。从服与承重。自是两项事。夫承重而其姑在。则妻虽从服。而不害为庶妇。嫡妇之名。依旧在姑。其承曾高祖之重者皆然。则其服乃庶妇之服。非承重之服。老先生答寒冈书。所谓其祖母或母服重服。妻不得承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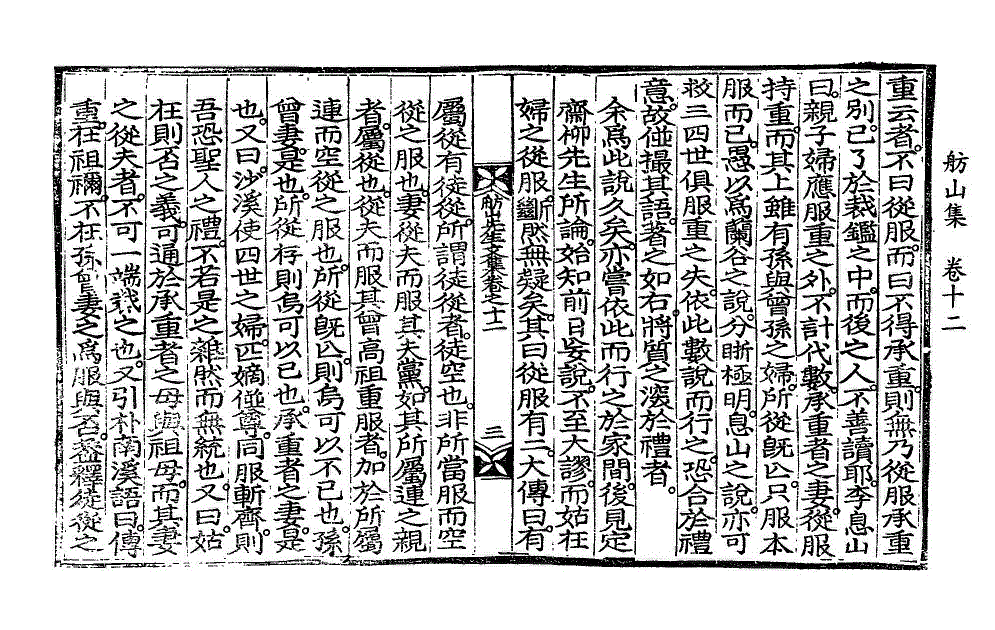 重云者。不曰从服。而曰不得承重。则无乃从服承重之别。已了于裁鉴之中。而后之人。不善读耶。李息山曰。亲子妇应服重之外。不计代数。承重者之妻。从服持重。而其上虽有孙与曾孙之妇。所从既亡。只服本服而已。愚以为兰谷之说。分䀸极明。息山之说。亦可救三四世俱服重之失。依此数说而行之。恐合于礼意。故并撮其语。著之如右。将质之深于礼者。
重云者。不曰从服。而曰不得承重。则无乃从服承重之别。已了于裁鉴之中。而后之人。不善读耶。李息山曰。亲子妇应服重之外。不计代数。承重者之妻。从服持重。而其上虽有孙与曾孙之妇。所从既亡。只服本服而已。愚以为兰谷之说。分䀸极明。息山之说。亦可救三四世俱服重之失。依此数说而行之。恐合于礼意。故并撮其语。著之如右。将质之深于礼者。余为此说久矣。亦尝依此而行之于家间。后见定斋柳先生所论。始知前日妄说。不至大谬。而姑在妇之从服。断然无疑矣。其曰从服有二。大传曰。有属从有徒从。所谓徒从者。徒空也。非所当服而空从之服也。妻从夫而服其夫党。如其所属连之亲者。属从也。从夫而服其曾高祖重服者。加于所属连而空从之服也。所从既亡。则乌可以不已也。孙曾妻。是也。所从存则乌可以已也。承重者之妻。是也。又曰。沙溪使四世之妇。匹嫡并尊。同服斩齐。则吾恐圣人之礼。不若是之杂然而无统也。又曰。姑在则否之义。可通于承重者之母与祖母。而其妻之从夫者。不可一端裁之也。又引朴南溪语曰。传重。在祖祢。不在孙曾妻之为服与否。盖释徒从之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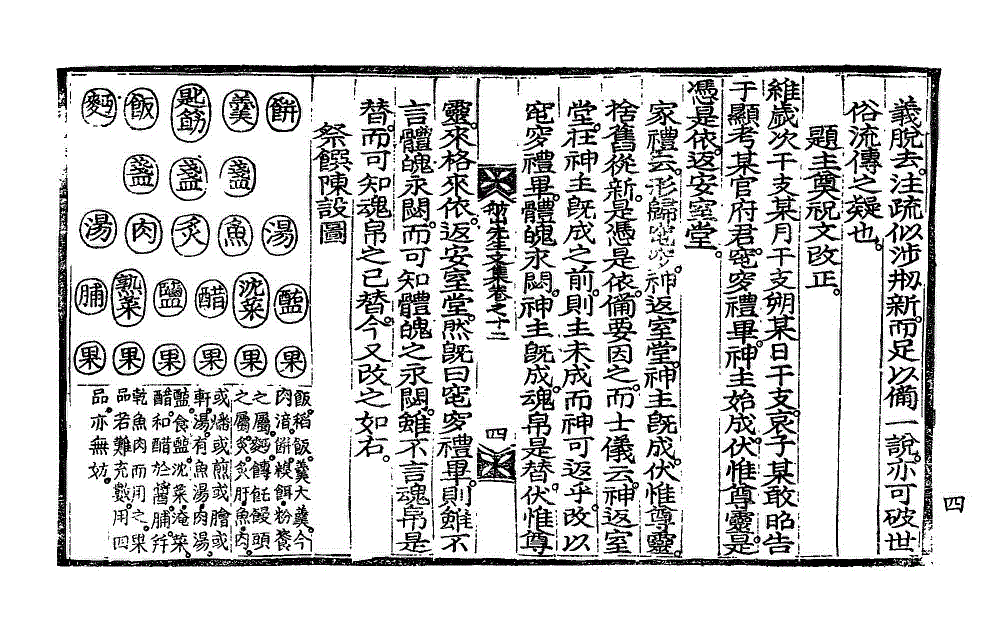 义脱去。注疏似涉刱新。而足以备一说。亦可破世俗流传之疑也。
义脱去。注疏似涉刱新。而足以备一说。亦可破世俗流传之疑也。题主奠祝文改正
维岁次干支某月干支朔某日干支。哀子某敢昭告于显考某官府君。窀穸礼毕。神主始成。伏惟尊灵。是凭是依。返安室堂。
家礼云。形归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备要因之。而士仪云。神返室堂。在神主既成之前。则主未成而神可返乎。改以窀穸礼毕。体魄永閟。神主既成。魂帛是替。伏惟尊灵。来格来依。返安室堂。然既曰窀穸礼毕。则虽不言体魄永閟。而可知体魄之永閟。虽不言魂帛是替。而可知魂帛之已替。今又改之如右。
祭馔陈设图
삽화 새창열기
(饭。稻饭。羹。大羹。今肉湆。饼。糗饵,粉餈之属。面。馎饦馒头之属。炙。炙肝,鱼,肉。或燔或煎或脍或轩。汤。有鱼汤,肉汤。醢。食醢。沈菜,淹菜。醋。和醋于酱。脯。并乾鱼肉而用之。果品若难充数。用四品。亦无妨。)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5H 页
 祭馔多品。出于流俗。非古人事神之礼也。神本湛一。其交也宜淡。既夕礼云。凡糗不煎。注。以膏煎之则亵不敬。是以退陶不许用油果。沙溪亦以油蜜果为非礼。诚以膏熬之臭。不若洁净。乱杂而陈。不若精简。则余虽违俗非罪。减品非刱。遂去繁馔。略依古式。乃作此图。以为私家遵用。
祭馔多品。出于流俗。非古人事神之礼也。神本湛一。其交也宜淡。既夕礼云。凡糗不煎。注。以膏煎之则亵不敬。是以退陶不许用油果。沙溪亦以油蜜果为非礼。诚以膏熬之臭。不若洁净。乱杂而陈。不若精简。则余虽违俗非罪。减品非刱。遂去繁馔。略依古式。乃作此图。以为私家遵用。朱子戒子曰。岁时享祀。汝辈及新妇等。切宜谨戒。凡祭肉脔割之馀。及皮毛之属。勿令残秽亵慢。刘氏琸曰。往者士大夫家妇女。皆亲涤祭器。造祭馔。近来妇女骄倨。不肯亲入庖厨。虽家有使令之人。亦须身亲监视。务令精洁。余乃书此。以戒子若妇也。
祔祭义
檀弓曰。殷。既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盖善殷。夫祔者。神之也。子之于亲。神之之遽。非人情也。孔子所以善殷也。然善之而已。非用之也。善之而非用之。何也。求之人情则殷善矣。用之者。时王之礼也。不可以不从周也。故曰盖善殷。盖者。未定之辞也。善殷而未定其辞。则可知其不用之也。若殷卒哭而祔。周练而祔。则孔子岂但善周而已。用之无疑也。然练而神之。人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5L 页
 子之心。犹有所不忍。不若终三年而神之也。若于孔子之时。有大祥而祔之礼。则其必为孔子之所善也。何以知之。推善殷而知之也。五礼仪曰。大祥祭毕。行祔祭。五礼仪者。今之国制。可从也。合乎人情。尤可从也。
子之心。犹有所不忍。不若终三年而神之也。若于孔子之时。有大祥而祔之礼。则其必为孔子之所善也。何以知之。推善殷而知之也。五礼仪曰。大祥祭毕。行祔祭。五礼仪者。今之国制。可从也。合乎人情。尤可从也。三年内墓祭说
家礼。虽无三年内墓祭之文。然寒冈先生曰。孝子于体魄所藏。虽三年之后。尚不堪雨露霜露之感。况坟土未乾之时乎。求之人情。固当如是。何可不祭。或曰。如虞,卒哭。三献读祝。或曰。坟土未乾之前。哀省为主。只如朔望奠。一献无祝。下段说亦可从。
丧中杂记
丧次之设。酒食待客。大不可。程子葬父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先生曰。勿陷人于恶。朱子曰。丧葬之时。只当以素食待客。退溪先生曰。世俗例于葬送祥祭之日。必设酒食以待吊客。客之无知者。或醉达朝。甚无谓也。盖三先生所戒。若此之严。而末俗益弊。凡于葬祥。必盛备酒食于祭馔之外。以馈客。有如宴集之时。岂不甚骇哉。此则决不可循俗也。若非祥祭之时。而吊客来宿。则其翌日。有难仍设素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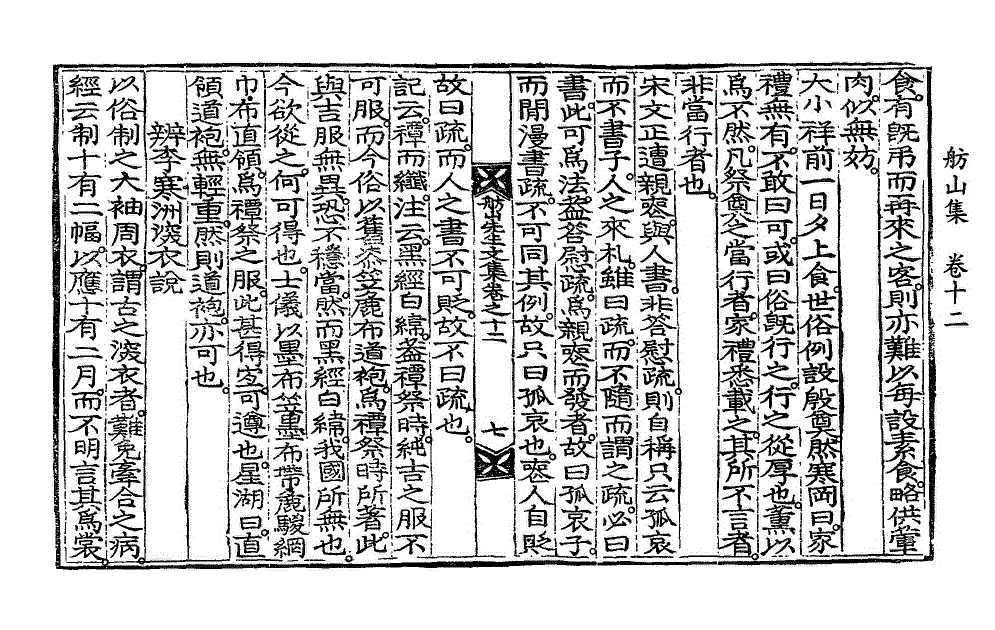 食。有既吊而再来之客。则亦难以每设素食。略供荤肉。似无妨。
食。有既吊而再来之客。则亦难以每设素食。略供荤肉。似无妨。大小祥前一日夕上食。世俗例设殷奠。然寒冈曰。家礼无有。不敢曰可。或曰俗既行之。行之从厚也。薰以为不然。凡祭奠之当行者。家礼悉载之。其所不言者。非当行者也。
宋文正遭亲丧。与人书。非答慰疏。则自称只云孤哀而不书子。人之来札。虽曰疏。而不随而谓之疏。必曰书。此可为法。盖答慰疏。为亲丧而发者。故曰孤哀子。而閒漫书疏。不可同其例。故只曰孤哀也。丧人自贬故曰疏。而人之书不可贬。故不曰疏也。
记云。禫而纤。注云。黑经白纬。盖禫祭时。纯吉之服不可服。而今俗以旧㓒笠粗布道袍。为禫祭时所著。此与吉服无异。恐不稳当。然而黑经白纬。我国所无也。今欲从之。何可得也。士仪以墨布笠,墨布带,粗騣网巾,布直领。为禫祭之服。此甚得宜。可遵也。星湖曰。直领道袍。无轻重。然则道袍。亦可也。
辨李寒洲深衣说
以俗制之大袖周衣。谓古之深衣者。难免牵合之病。经云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而不明言其为裳。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6L 页
 郑注。始以裳言之。故今以大袖周衣之用布十二幅当之。而斥注家为傅会。若尔则朱子家礼深衣之制。亦狃于汉儒。而不得其古者也。世多以家礼未经朱子再勘为疑。然大全载深衣图。而与家礼少无异焉。则盖衣裳之各幅缝联。自古如此矣。汉儒去古未远。仪文度数之辨。详于后世。故此等处。朱子亦从之。末俗好新。不合吾见。则虽古人文字。便开口大谈。谓以傅会。无乃不思也乎。愚遂反复古经。知十有二幅之专就裳制说也。经曰。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详其文势。此五者各为一件。非以上一句。统论全衣也。且以齐倍要推之。则衣裳之缝界分明。然后可以定要中之数。而齐之倍要。亦可得矣。如以十二幅通言衣裳。则衣与裳一布相连。而其当要处。可上可下。固难的指也。况所谓衣身正幅。各广尺二寸。垂前后长及踝。则要齐之数同矣。下衽斜裁六幅。属之衣傍。而腋下各二幅。领下各一幅。使之齐倍于要云者。亦甚苟矣。腋下之幅。上太尖而下太广。全不成法。象其参差不齐之状。何可以应先王正朔耶。
郑注。始以裳言之。故今以大袖周衣之用布十二幅当之。而斥注家为傅会。若尔则朱子家礼深衣之制。亦狃于汉儒。而不得其古者也。世多以家礼未经朱子再勘为疑。然大全载深衣图。而与家礼少无异焉。则盖衣裳之各幅缝联。自古如此矣。汉儒去古未远。仪文度数之辨。详于后世。故此等处。朱子亦从之。末俗好新。不合吾见。则虽古人文字。便开口大谈。谓以傅会。无乃不思也乎。愚遂反复古经。知十有二幅之专就裳制说也。经曰。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详其文势。此五者各为一件。非以上一句。统论全衣也。且以齐倍要推之。则衣裳之缝界分明。然后可以定要中之数。而齐之倍要。亦可得矣。如以十二幅通言衣裳。则衣与裳一布相连。而其当要处。可上可下。固难的指也。况所谓衣身正幅。各广尺二寸。垂前后长及踝。则要齐之数同矣。下衽斜裁六幅。属之衣傍。而腋下各二幅。领下各一幅。使之齐倍于要云者。亦甚苟矣。腋下之幅。上太尖而下太广。全不成法。象其参差不齐之状。何可以应先王正朔耶。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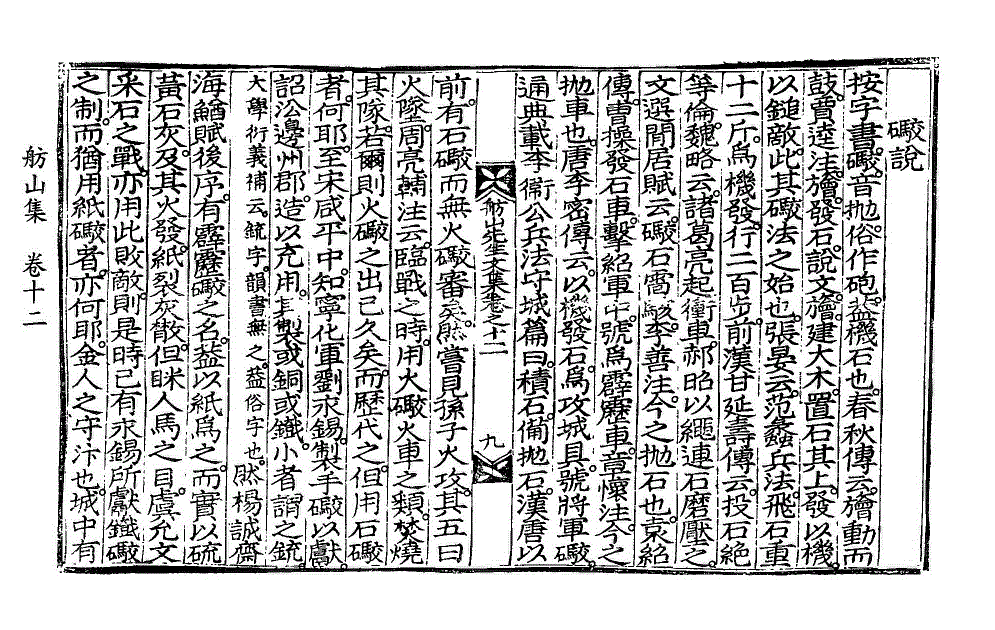 炮说
炮说按字书。炮。音抛。俗作炮。盖机石也。春秋传云。旝动而鼓。贾逵注。旝。发石。说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锤敌。此其炮法之始也。张晏云。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前汉甘延寿传云。投石绝等伦。魏略云。诸葛亮起冲车。郝昭以绳连石磨压之。文选閒居赋云。炮石雷骇。李善注。今之抛石也。袁绍传。曹操发石车。击绍军中。号为霹雳车。章怀注。今之抛车也。唐李密传云。以机发石。为攻城具。号将军炮。通典载李卫公兵法守城篇曰。积石。备抛石。汉唐以前。有石炮而无火炮审矣。然尝见孙子火攻。其五曰火坠。周亮辅注云。临战之时。用火炮火车之类。焚烧其队。若尔则火炮之出已久矣。而历代之。但用石炮者。何耶。至宋咸平中。知宁化军刘永锡。制手炮以献。诏沿边州郡。造以充用。其制或铜或铁。小者谓之铳。(大学衍义补云。铳字。韵书无之。盖俗字也。)然杨诚斋海䲡赋后序。有霹雳炮之名。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硫黄石灰。及其火发。纸裂灰散。但眯人马之目。虞允文采石之战。亦用此败敌。则是时已有永锡所献铁炮之制。而犹用纸炮者。亦何耶。金人之守汴也。城中有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7L 页
 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声发如雷。而制犹未工。及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炮法。攻破襄阳。火炮之用。于是甚精。然造法不传。 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鎗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而亦未传习于外间。嘉靖八年。始造佛郎(即佛兰西。)机炮。而诸边镇皆知制造之法。(明史兵志。佛郎机炮大者。重千斤。巨腹长颈。贮药腹中。发及百馀丈。最利于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万历时。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西洋夷毛发皆红。故曰红夷。)然启祯野乘云。有薄珏者刱意造铜炮铁丸。所过三军薤粉。则不待西夷。而巨炮之造。已刱于中国也。我东则自胜国。已有火炮。郑地以此焚倭船云。而此制不传。于我国壬辰之乱。倭人以火炮长驱。八域糜烂几尽。无亦气数之使然耶。 宣祖己丑。日本平义智来献鸟铳数件。我国之有鸟铳始此。然不晓其制。未几而彼兵出矣。至癸巳。因戚将军继光纪效新书。刱置训营。使军兵学习鸟铳。亦解煮硝之法。而无及于乱矣。岂非亡羊而补牢耶。 仁祖辛未。陈奏使郑斗源入燕京。逢洋人陆若汉。得一火炮而来。岁久远。不知其藏在武库与不也。近见清人所载炮式。则有百子连珠炮,
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声发如雷。而制犹未工。及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炮法。攻破襄阳。火炮之用。于是甚精。然造法不传。 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鎗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而亦未传习于外间。嘉靖八年。始造佛郎(即佛兰西。)机炮。而诸边镇皆知制造之法。(明史兵志。佛郎机炮大者。重千斤。巨腹长颈。贮药腹中。发及百馀丈。最利于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万历时。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西洋夷毛发皆红。故曰红夷。)然启祯野乘云。有薄珏者刱意造铜炮铁丸。所过三军薤粉。则不待西夷。而巨炮之造。已刱于中国也。我东则自胜国。已有火炮。郑地以此焚倭船云。而此制不传。于我国壬辰之乱。倭人以火炮长驱。八域糜烂几尽。无亦气数之使然耶。 宣祖己丑。日本平义智来献鸟铳数件。我国之有鸟铳始此。然不晓其制。未几而彼兵出矣。至癸巳。因戚将军继光纪效新书。刱置训营。使军兵学习鸟铳。亦解煮硝之法。而无及于乱矣。岂非亡羊而补牢耶。 仁祖辛未。陈奏使郑斗源入燕京。逢洋人陆若汉。得一火炮而来。岁久远。不知其藏在武库与不也。近见清人所载炮式。则有百子连珠炮,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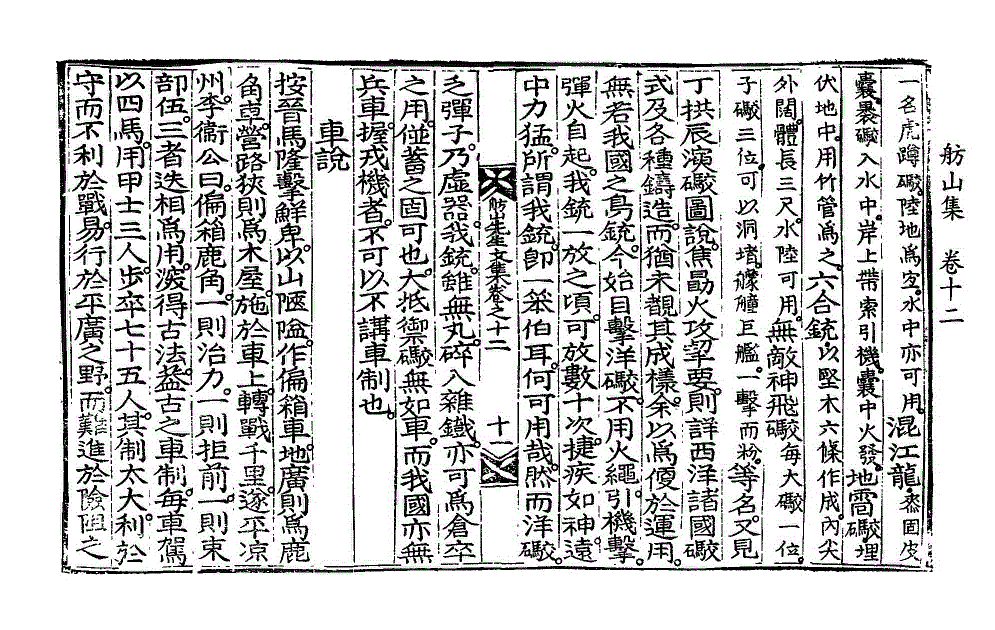 (一名虎蹲炮。陆地为宜。水中亦可用。)混江龙,(桼固皮囊。裹炮入水中。岸上带索引机。囊中火发。)地雷炮,(埋伏地中。用竹管为之。)六合铳,(以坚木六条作成。内尖外阔。体长三尺。水陆可用。)无敌神飞炮(每大炮一位。子炮三位。可以洞堵。艨艟巨舰。一击而粉。)等名。又见丁拱辰演炮图说。焦勖火攻挈要。则详西洋诸国炮式及各种铸造。而犹未睹其成样。余以为便于运用。无若我国之鸟铳。今始目击洋炮。不用火绳。引机击。弹火自起。我铳一放之顷。可放数十次。捷疾如神。远中力猛。所谓我铳。即一笨伯耳。何可用哉。然而洋炮。乏弹子。乃虚器。我铳。虽无丸。碎入杂铁。亦可为仓卒之用。并蓄之固可也。大抵御炮无如车。而我国亦无兵车。握戎机者。不可以不讲车制也。
(一名虎蹲炮。陆地为宜。水中亦可用。)混江龙,(桼固皮囊。裹炮入水中。岸上带索引机。囊中火发。)地雷炮,(埋伏地中。用竹管为之。)六合铳,(以坚木六条作成。内尖外阔。体长三尺。水陆可用。)无敌神飞炮(每大炮一位。子炮三位。可以洞堵。艨艟巨舰。一击而粉。)等名。又见丁拱辰演炮图说。焦勖火攻挈要。则详西洋诸国炮式及各种铸造。而犹未睹其成样。余以为便于运用。无若我国之鸟铳。今始目击洋炮。不用火绳。引机击。弹火自起。我铳一放之顷。可放数十次。捷疾如神。远中力猛。所谓我铳。即一笨伯耳。何可用哉。然而洋炮。乏弹子。乃虚器。我铳。虽无丸。碎入杂铁。亦可为仓卒之用。并蓄之固可也。大抵御炮无如车。而我国亦无兵车。握戎机者。不可以不讲车制也。车说
按晋马隆击鲜卑。以山狭隘。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千里。遂平凉州。李卫公曰。偏箱鹿角。一则治力。一则拒前。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深得古法。盖古之车制。每车驾以四马。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易行于平广之野。而难进于险阻之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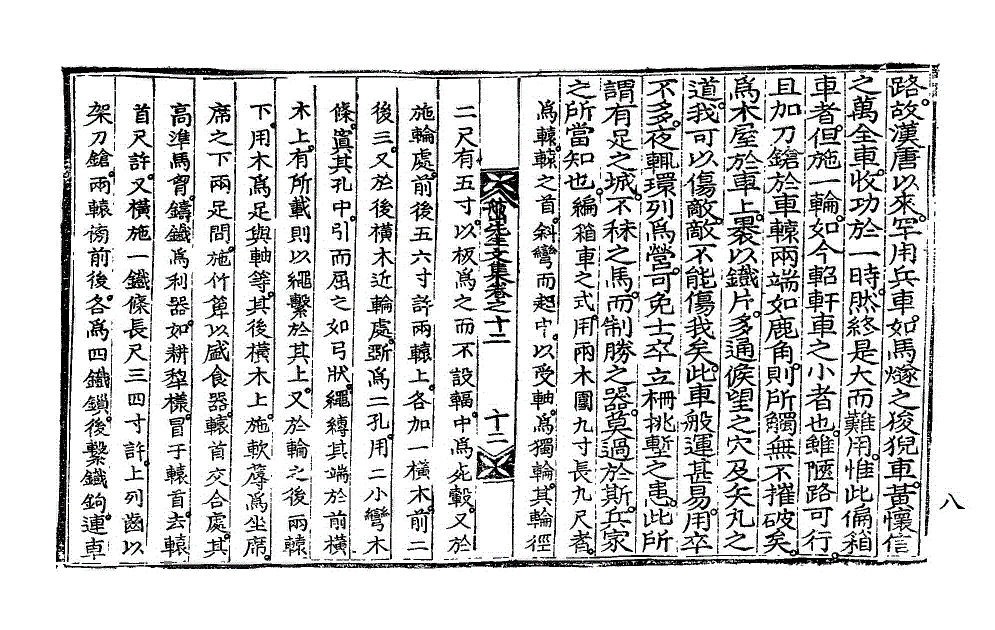 路。故汉唐以来。罕用兵车。如马燧之狻猊车。黄怀信之万全车。收功于一时。然终是大而难用。惟此偏箱车者。但施一轮。如今轺轩车之小者也。虽狭路可行。且加刀鎗于车辕两端如鹿角。则所触无不摧破矣。为木屋于车上。裹以铁片。多通候望之穴及矢丸之道。我可以伤敌。敌不能伤我矣。此车般运甚易。用卒不多。夜辄环列为营。可免士卒立栅挑堑之患。此所谓有足之城。不秣之马。而制胜之器。莫过于斯。兵家之所当知也。(编箱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 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斲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寘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箄以盛食器。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辕首。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鎗。两辕傍前后。各为四铁锁。后系铁钩。连车
路。故汉唐以来。罕用兵车。如马燧之狻猊车。黄怀信之万全车。收功于一时。然终是大而难用。惟此偏箱车者。但施一轮。如今轺轩车之小者也。虽狭路可行。且加刀鎗于车辕两端如鹿角。则所触无不摧破矣。为木屋于车上。裹以铁片。多通候望之穴及矢丸之道。我可以伤敌。敌不能伤我矣。此车般运甚易。用卒不多。夜辄环列为营。可免士卒立栅挑堑之患。此所谓有足之城。不秣之马。而制胜之器。莫过于斯。兵家之所当知也。(编箱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 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斲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寘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箄以盛食器。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辕首。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鎗。两辕傍前后。各为四铁锁。后系铁钩。连车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9H 页
 为营之际。彼此相维以为固。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鎗以夹持之。○按此车制。载纪效书中。而若欲置木屋于车上。则略加变通然后可也。)
为营之际。彼此相维以为固。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鎗以夹持之。○按此车制。载纪效书中。而若欲置木屋于车上。则略加变通然后可也。)书裴翁说
邻里有裴翁。凡民之年高者也。年八十九。无疾恙。步履便旋如少时。子孙皆勤耕而食足云。一日来见。余与之酒。仍问曰。何以寿也。曰。至畏者。天也。人不知天之可畏。富者。自谓长如此。不能撙节。侈汰为事。失其富。贵者。自夸显荣。怙势骄人。无所忌惮。不保其贵。使其子孙。无以糊其口。失所流离。皆获憎于天而然也。某虽无识。每祝天曰。使我无害人心。使我无生贪欲。夫多欲之人多败。欲害人者。害先归于己。天道昭昭。报施不差。地上何物。不系于天。何事天不监之耶。平生知畏天而已。余闻而敬之曰。玆其所以得高年也。士大夫之读书谈义理者。其知天几希。滔滔末俗。尽入于利欲窠臼。悖天理而沦天性。戕生而覆家者何限。彼以闾巷一老。其言类知道者。诚可异也。天锡黄耇。安乐无灾。讵不宜哉。
芝泉草木志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9L 页
 山园涔寂。无所托悰。遂列植卉木之冬青多寿者。馨香芳洁者。佳果可餐者。仍识之。
山园涔寂。无所托悰。遂列植卉木之冬青多寿者。馨香芳洁者。佳果可餐者。仍识之。松百木之长。贯四时。不改柯易叶。松脂一名松肪。入地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大松千岁。其精变为青牛。或为伏龟。叶曰针。我国之海松子。即五针松也。其实润五脏。治骨节风。俗号柏子。沿习之谬也。白松皮。如霜雪色。
竹璇玑玉精。受气于玄轩之宿。广志曰。云母大竹也。
柏。尔雅曰。掬也。禹贡。荆州贡柏。得金之正气。故其枝西向。柏茶止血滋阴。
桧说文曰。柏叶松身。太清宫记云。太清宫桧。老子手植。根株枝干。皆左纫。李唐兴。一枝再生。宋时。亦有此异。苏轼诗。汝阴多老桧。处处屯苍云。地连丹砂井。物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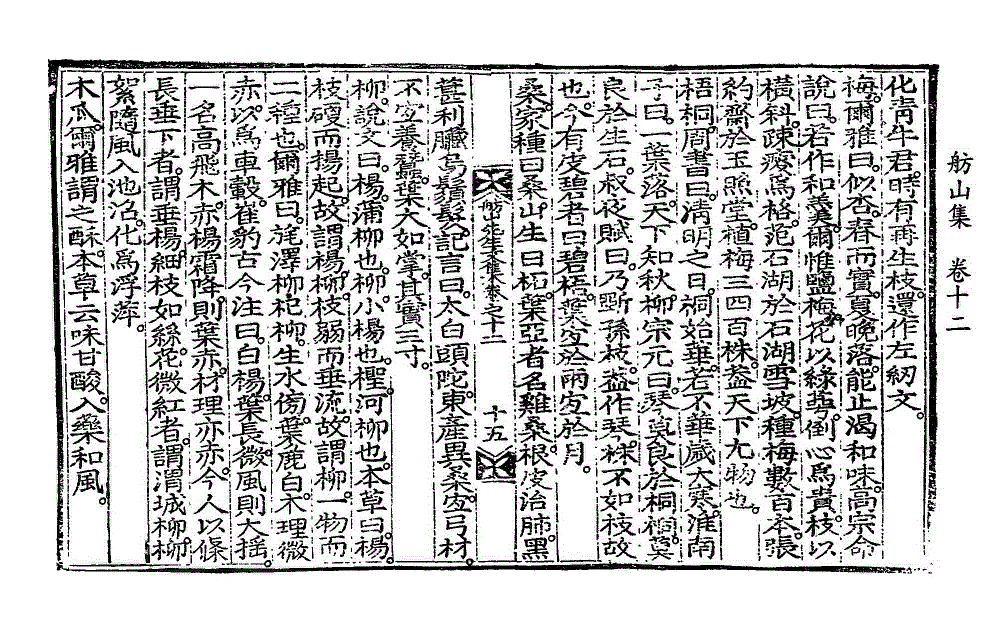 化青牛君。时有再生枝。还作左纫文。
化青牛君。时有再生枝。还作左纫文。梅。尔雅曰。似杏。春而实。夏晚落。能止渴和味。高宗命说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花以绿萼。倒心为贵。枝以横斜。疏瘦为格。范石湖于石湖雪坡。种梅数百本。张约斋于玉照堂。植梅三四百株。盖天下尤物也。
梧桐。周书曰。清明之日。桐始华。若不华岁大寒。淮南子曰。一叶落。天下知秋。柳宗元曰。琴莫良于桐桐。莫良于生石。叔夜赋曰。乃斲孙枝。盖作琴。株不如枝故也。今有皮碧者曰碧梧。叶宜于两宜于月。
桑。家种曰桑。山生曰柘。叶亚者名鸡桑。根皮治肺。黑葚利脏乌须发。记言曰。太白头陀。东产异桑。宜弓材。不宜养蚕。叶大如掌。其实三寸。
柳。说文曰。杨。蒲柳也。柳。小杨也。柽。河柳也。本草曰。杨。枝硬而扬起。故谓杨。柳。枝弱而垂流。故谓柳。一物而二种也。尔雅曰。旄泽柳,杞柳。生水傍。叶粗白。木理微赤。以为车毂。崔豹古今注曰。白杨。叶长。微风则大摇。一名高飞木。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今人以条长垂下者。谓垂杨。细枝如丝。花微红者。谓渭城柳。柳絮随风入池沼。化为浮萍。
木瓜。尔雅谓之酥。本草云味甘酸。入药和风。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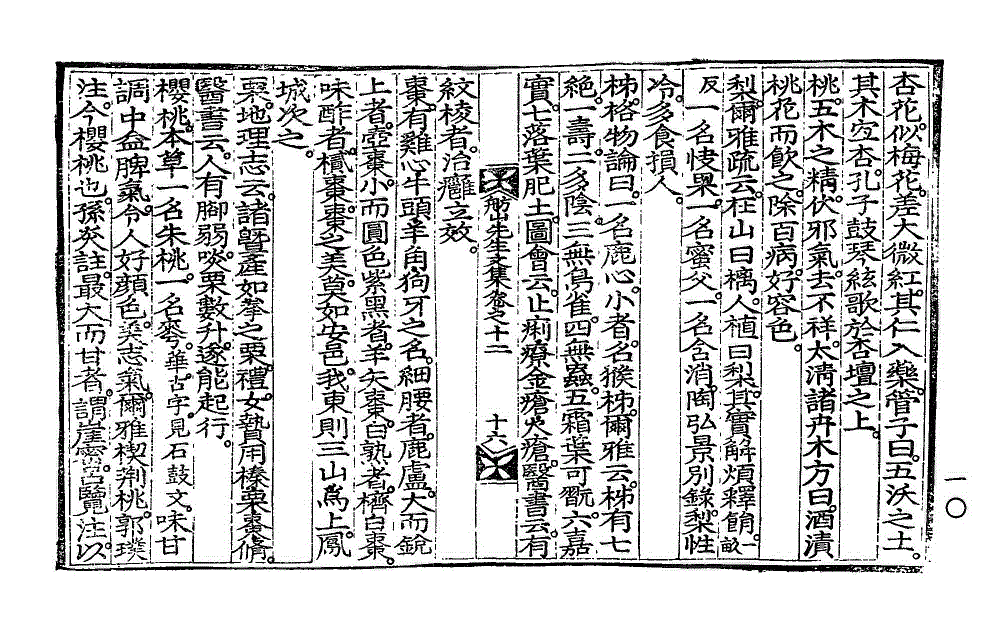 杏花。似梅花。差大微红。其仁入药。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孔子鼓琴弦歌于杏坛之上。
杏花。似梅花。差大微红。其仁入药。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孔子鼓琴弦歌于杏坛之上。桃。五木之精。伏邪气。去不祥。太清诸卉木方曰。酒渍桃花而饮之。除百病。好容色。
梨。尔雅疏云。在山曰樆。人植曰梨。其实解烦释䬼。(一亩反)一名快果。一名蜜父。一名含消。陶弘景别录。梨性冷。多食损人。
柹。格物论曰。一名鹿心。小者。名猴柹。尔雅云。柹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雀。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土。图会云。止痢,疗金疮,火疮。医书云。有纹棱者。治痈立效。
枣。有鸡心,牛头,羊角,狗牙之名。细腰者。鹿卢。大而锐上者。壶枣。小而圆色紫黑者。羊矢枣。白熟者。櫅白枣。味酢者。樲枣。枣之美。莫如安邑。我东则三山为上。凤城次之。
栗。地理志云。诸暨产如拳之栗。礼。女贽用榛,栗,枣,脩。医书云。人有脚弱。啖栗数升。遂能起行。
樱桃。本草一名朱桃。一名▼(来/兮)。(华。古字。见石鼓文。)味甘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志气。尔雅楔荆桃。郭璞注。今樱桃也。孙炎注。最大而甘者。谓崖密。吕览注。以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1H 页
 莺所含食。故曰含桃。盖先百果含荣者也。月令云。仲夏之月。以樱桃。先荐寝庙。
莺所含食。故曰含桃。盖先百果含荣者也。月令云。仲夏之月。以樱桃。先荐寝庙。胡桃。张骞使外国还。乃得胡桃种。薄皮多肌。实亦有房。瓤白味甘。能治肺气。
石榴。五月花开。花有黄赤二色。实有甘酸苦三种。潘岳赋。千房同膜。十子如一。御饥疗疾。解酲止渴。道家谓三尸酒。以三尸得此果则醉也。出自涂林安石国。故名石榴。一名丹若。左思蜀都赋。若榴竞裂。
莲芙蕖。其茎茄。其叶蕸。其花菡萏。其实莲。其本蔤。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花有红白。有重台者。并头者。人指以为瑞。白房上尖。有红晕者。谓鹤顶红。出于钱塘。故一名钱塘红。楚辞言缉以为裳。取其芳洁。濂溪先生作爱莲说。
菊。月令季秋。菊有黄华。花以黄为上。白次之。红又次之。茎紫者。味甘入药。茎青者。味苦。非真菊也。屈原嗜之。渊明尤爱之。南阳郦县人。饮菊水。寿百馀岁。陆龟蒙,苏东坡,张南轩。皆有赋。南轩云。中和所萃。颓龄之可制。李时珍曰。菊品凡百种。刘蒙泉著菊谱。颇详。然亦不能尽载。
牧丹。唐人称为木芍药。又名百两金。其品颇多。姚黄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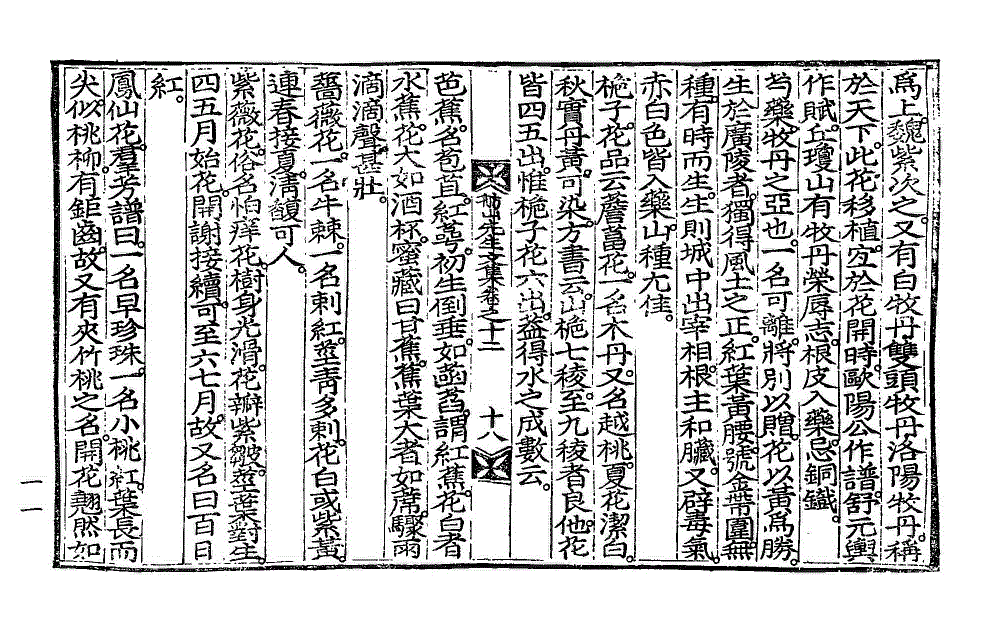 为上。魏紫次之。又有白牧丹,双头牧丹,洛阳牧丹。称于天下。此花移植。宜于花开时。欧阳公作谱。舒元舆作赋。丘琼山有牧丹荣辱志。根皮入药。忌铜铁。
为上。魏紫次之。又有白牧丹,双头牧丹,洛阳牧丹。称于天下。此花移植。宜于花开时。欧阳公作谱。舒元舆作赋。丘琼山有牧丹荣辱志。根皮入药。忌铜铁。芍药。牧丹之亚也。一名可离。将别以赠。花以黄为胜。生于广陵者。独得风土之正。红叶黄腰。号金带围。无种。有时而生。生则城中出宰相。根主和脏。又辟毒气。赤白色皆入药。山种尤佳。
栀子。花品云薝葍花。一名木丹。又名越桃。夏花洁白。秋实丹黄。可染。方书云。山栀七棱。至九棱者良。他花皆四五出。惟栀子花六出。盖得水之成数云。
芭蕉。名苞苴。红萼。初生倒垂。如菡萏。谓红蕉。花白者水蕉。花大如酒杯。蜜藏曰甘蕉。蕉叶大者如席。骤雨滴滴声。甚壮。
蔷薇花。一名牛棘。一名刺红。茎青多刺。花白或紫黄。连春接夏。清馥可人。
紫薇花。俗名怕痒花。树身光滑。花瓣紫皱。茎叶对生。四五月始花。开谢接续。可至六七月。故又名曰百日红。
凤仙花。群芳谱曰。一名早珍珠。一名小桃红。叶长而尖。似桃柳。有钜齿。故又有夹竹桃之名。开花翘然如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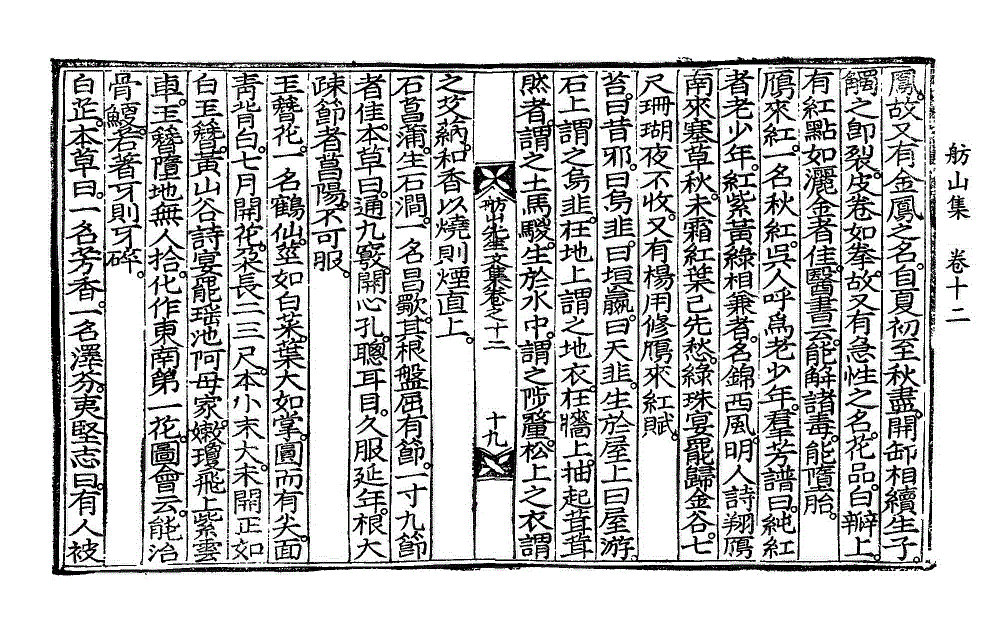 凤。故又有金凤之名。自夏初至秋尽。开卸相续生子。触之即裂。皮卷如拳。故又有急性之名。花品。白瓣上。有红点如洒金者佳。医书云。能解诸毒。能堕胎。
凤。故又有金凤之名。自夏初至秋尽。开卸相续生子。触之即裂。皮卷如拳。故又有急性之名。花品。白瓣上。有红点如洒金者佳。医书云。能解诸毒。能堕胎。雁来红。一名秋红。吴人呼为老少年。群芳谱曰。纯红者老少年。红紫黄录相兼者。名锦西风。明人诗翔雁南来塞草秋。未霜红叶已先愁。绿珠宴罢归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又有杨用修雁来红赋。
苔。曰昔邪。曰乌韭。曰垣嬴。曰天韭。生于屋上曰屋游。石上谓之乌韭。在地上谓之地衣。在墙上。抽起茸茸然者。谓之土马騣。生于水中。谓之陟釐。松上之衣谓之艾蒳。和香以烧则烟直上。
石菖蒲。生石涧。一名昌歜。其根盘屈有节。一寸九节者佳。本草曰。通九窍。开心孔。聪耳目。久服延年。根大疏节者菖阳。不可服。
玉簪花。一名鹤仙。茎如白菜。叶大如掌。圆而有尖。面青背白。七月开花。朵长二三尺。本小末大。未开正如白玉簪。黄山谷诗宴罢瑶池阿母家。嫩琼飞上紫云车。玉簪堕地无人拾。化作东南第一花。图会云。能治骨鲠。若著牙则牙碎。
白芷。本草曰。一名芳香。一名泽芬。夷坚志曰。有人被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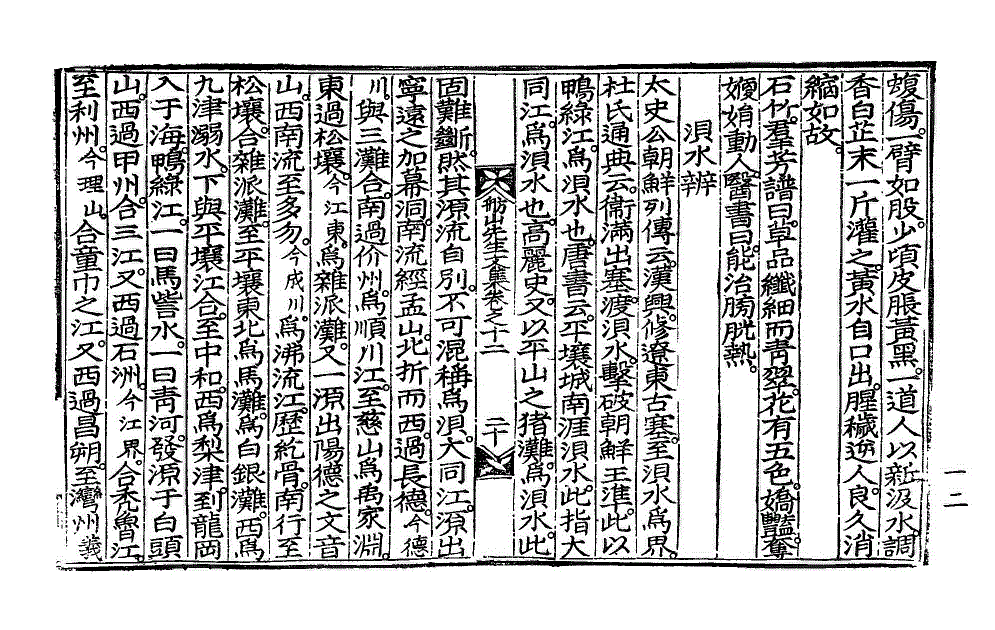 蝮伤。一臂如股。少顷皮胀黄黑。一道人以新汲水。调香白芷末一斤灌之。黄水自口出。腥秽逆人。良久消缩如故。
蝮伤。一臂如股。少顷皮胀黄黑。一道人以新汲水。调香白芷末一斤灌之。黄水自口出。腥秽逆人。良久消缩如故。石竹。群芳谱曰。草品纤细而青翠。花有五色。娇艳。夺㛹娟动人。医书曰。能治膀胱热。
浿水辨
太史公朝鲜列传云。汉兴。修辽东古塞。至浿水为界。杜氏通典云。卫满出塞。渡浿水。击破朝鲜王准。此以鸭绿江。为浿水也。唐书云。平壤城南涯浿水。此指大同江。为浿水也。高丽史。又以平山之猪滩。为浿水。此固难断。然其源流自别。不可混称为浿。大同江。源出宁远之加幕洞。南流经孟山。北折而西。过长德。(今德川。)与三滩合。南过价州。为顺川江。至慈山为禹家渊。东过松壤。(今江东。)为杂派滩。又一源出阳德之文音山。西南流至多勿。(今成川。)为沸流江。历纥骨。南行至松壤。合杂派滩。至平壤东北为马滩。为白银滩。西为九津溺水。下与平壤江合。至中和。西为梨津。到龙冈入于海。鸭绿江。一曰马訾水。一曰青河。发源于白头山。西过甲州。合三江。又西过石洲。(今江界。)合秃鲁江。至利州。(今理山。)合童巾之江。又西过昌朔。至湾州(义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3H 页
 州)之北。分为三派。南汇为九龙之渊。西为西江。中为小西江。又合为黔同之岛。又分而为二。西会狄江。南为大江。又合而为大总江。入西海。猪滩之源。出遂安彦真山。过覃州。(今新溪)北为歧滩。东为箭滩。至平山而为猪滩。过牛峰。与蛤滩合流。其源不同。有如是矣。阚骃十三州志云。浿水县在乐浪东北。斑志云。浿水西至增地县入海。增地。龙冈古号也。乐浪。平壤也。又按纲目。隋将军来护儿。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则浿水之近于平壤验矣。且我国之人。举知大同江之为浿水。以其相沿而习闻故也。太史所云。未曾目击。只依传说而记之。则易有差谬。丽史所云。百济始祖自慰礼城。(稷山)移都汉山。以浿水为界。是时高句丽都于平壤。岂以城傍之水。为百济境。必指猪滩为浿。此若可信。而猪滩之为浿说者寡。大同之为浿说者众。说者寡而其微可知尔也。说者众而其著可知尔也。余姑从其著焉。
州)之北。分为三派。南汇为九龙之渊。西为西江。中为小西江。又合为黔同之岛。又分而为二。西会狄江。南为大江。又合而为大总江。入西海。猪滩之源。出遂安彦真山。过覃州。(今新溪)北为歧滩。东为箭滩。至平山而为猪滩。过牛峰。与蛤滩合流。其源不同。有如是矣。阚骃十三州志云。浿水县在乐浪东北。斑志云。浿水西至增地县入海。增地。龙冈古号也。乐浪。平壤也。又按纲目。隋将军来护儿。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则浿水之近于平壤验矣。且我国之人。举知大同江之为浿水。以其相沿而习闻故也。太史所云。未曾目击。只依传说而记之。则易有差谬。丽史所云。百济始祖自慰礼城。(稷山)移都汉山。以浿水为界。是时高句丽都于平壤。岂以城傍之水。为百济境。必指猪滩为浿。此若可信。而猪滩之为浿说者寡。大同之为浿说者众。说者寡而其微可知尔也。说者众而其著可知尔也。余姑从其著焉。东海碑注
碑眉叟许先生作也。先生尝上劄。辨正邦礼。为异议者挤斥。出守陟州。地滨海。先生乃撰东海之颂。用古文书诸石。立于汀罗岛上。首言瀛海之为百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3L 页
 川宗。中言物产之珍怪。蛮夷之杂种。终言古圣之世。德被广博。虽绝党殊俗。无不同囿。咸育于大化之中。而慨今时之遗风太邈。其寓感深矣。不知者称为退潮碑。此甚可笑。我邦之东北海。本无潮汐。故碑文既言其无。则有何可退者乎。朴薰卿氏。尝注此碑。援据虽赅。多引僻奥。反漏的證。故余遂改释如左。癸未孟冬。
川宗。中言物产之珍怪。蛮夷之杂种。终言古圣之世。德被广博。虽绝党殊俗。无不同囿。咸育于大化之中。而慨今时之遗风太邈。其寓感深矣。不知者称为退潮碑。此甚可笑。我邦之东北海。本无潮汐。故碑文既言其无。则有何可退者乎。朴薰卿氏。尝注此碑。援据虽赅。多引僻奥。反漏的證。故余遂改释如左。癸未孟冬。陟州。古悉直氏之地。
按东史。新罗婆娑王时。悉直国来降。智證王六年。为州置军主。高丽成宗时。改为陟州。今三陟府。
獩墟。
獩或作秽。汉元朔元年。秽君南闾降。为沧海郡。文献备考。今江陵东。有秽时所筑古城遗址。
瀛海漭瀁。
史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有裨海环之。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瀁水无涯也。左思吴都赋。澒洞沆瀁。
东北沙海。无潮无汐。号为大泽。
按先生陟州记事。东海沙海。无沮洳卑湿之气。然则水易渗泄。而不能为潮也。星湖僿说云。白头之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4H 页
 山。自肃慎境。一干南行。连亘于庆尚道日本之地。北接胡地。遮拦东南海口。潮势不能及。亦可备一说。然万流归东。如人身之水谷。必归膀胱。有疏下而无逆上。故东海所以无潮汐。非专由于山势之转抱也。
山。自肃慎境。一干南行。连亘于庆尚道日本之地。北接胡地。遮拦东南海口。潮势不能及。亦可备一说。然万流归东。如人身之水谷。必归膀胱。有疏下而无逆上。故东海所以无潮汐。非专由于山势之转抱也。浡潏。
水沸涌貌。木华海赋。天纲浡潏。
汪濊。
濊。韵书。呼会切。水深广也。前汉郊祀歌。泽汪濊。
海动有曀。
记言云。东海常多大风。波浪拍岸十丈。惟西风海静。然厉风则海动。或无风波浪。谓之海恶。尔雅。阴而风曰曀。
明明旸谷。太阳之门。羲伯司宾。
旸谷。日出处。羲伯。即尧典所谓羲仲也。尧命之以导日出。宾。是导引之义。
析木。
尔雅。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
牝牛之宫。
星家以箕尾之躔。谓牝牛宫。盖其躔次在丑方故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4L 页
 也。或曰。易离卦云。畜牝牛吉。盖离之为体柔顺。有似乎牝牛。以先天方位言之。则离在东。而离为日之象。故东海日出处。谓牝牛宫。可备一说。术书又云。牝牛东海神名。
也。或曰。易离卦云。畜牝牛吉。盖离之为体柔顺。有似乎牝牛。以先天方位言之。则离在东。而离为日之象。故东海日出处。谓牝牛宫。可备一说。术书又云。牝牛东海神名。日本无东。
日本。日所出之本。此是东之极也。
鲛人。
任昉述异记。鲛人。水居如鱼。不废机织。泣则成珠。
汗汗。
郭璞江赋。汗汗沺沺。水广大无涯貌。
漫漫。
水经注。漫漫。长远貌。
奇物谲诡。宛宛之祥。兴德而章。
按司马相如封禅书。奇物谲诡。倜傥穷变。又云宛宛黄龙。兴德而章。胡广云。宛宛屈伸也。
蚌之胎珠。
吕氏春秋。月望则蚌蛤实。左思吴都赋。蚌蛤珠胎与月亏全。
天吴九首。
山海经云。朝阳谷。有神曰天吴。是为水伯。虎身人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5H 页
 面。八首八足八尾。青黄色。今云九首恐误。
面。八首八足八尾。青黄色。今云九首恐误。怪夔一股。
山海经东海中。有流山。入海七千里。有兽。状如牛。苍身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名夔。
轇轧。
轧。说文。车辗也。言日轮如车辗而升。
炫熿。
玉篇。炫。光耀也。战国策云。炫熿于道。
沧沧。
说文。沧。寒也。列子云。日初出时。沧沧凉凉。及日中如探汤。近者热而远者凉。逸周书云。天地之道。有沧热。
三五月盈。
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郑注。三五者。播五行于四时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为十五之成数也。
水镜圆灵。
谢庄月赋。水镜。月。圆灵。天也。
扶桑沙华。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5L 页
 扶桑在大汉国东。其土多扶桑。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赪。绩其皮以为衣。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沙华公国。在东南海中。其国人。常出大海。劫夺人。卖怜阇沙国。
扶桑在大汉国东。其土多扶桑。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赪。绩其皮以为衣。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沙华公国。在东南海中。其国人。常出大海。劫夺人。卖怜阇沙国。黑齿麻罗。
记言。黑齿列传云。黑齿者。东海蛮国。亦曰日本之倭。其俗贵人漆齿。妇人亦漆齿。故曰黑齿之夷。按三才图会。近佛国。在东南海中。多野岛。蛮贼居之。号麻罗奴。商舶至其国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人。头为食器。非人类也。
撮髻莆家。
图会。莆家。龙在海东南。国王撮发脑后。人民剃头。
蜒蛮之蚝。
图会。蜒蛮有三种。一为鱼蜒。善举竿垂纶。一为蚝蜒。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蜒。伐木取果。盖贫国也。
瓜蛙之猴。
蛙。一作哇。续文献通考。瓜哇。即古婆娑国。土产多猿猴。
佛齐之牛。
宋史三佛齐。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在真腊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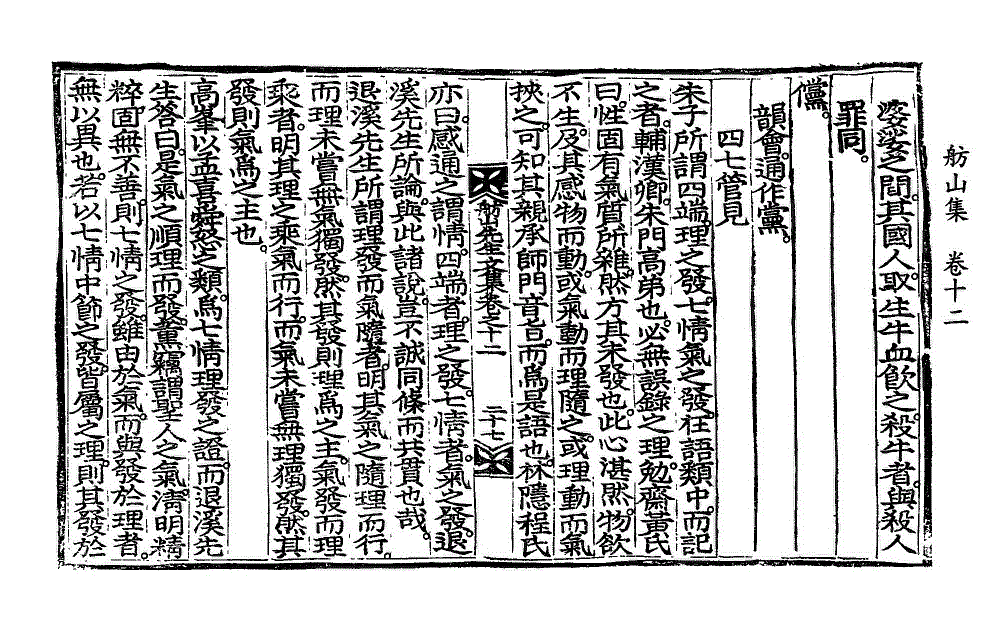 婆娑之间。其国人。取生牛血饮之。杀牛者。与杀人罪同。
婆娑之间。其国人。取生牛血饮之。杀牛者。与杀人罪同。傥。
韵会。通作党。
四七管见
朱子所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在语类中。而记之者。辅汉卿。朱门高弟也。必无误录之理。勉斋黄氏曰。性固有气质所杂。然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及其感物而动。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可知其亲承师门音旨。而为是语也。林隐程氏亦曰。感通之谓情。四端者。理之发。七情者。气之发。退溪先生所论。与此诸说。岂不诚同条而共贯也哉。
退溪先生所谓理发而气随者。明其气之随理而行。而理未尝无气独发。然其发则理为之主。气发而理乘者。明其理之乘气而行。而气未尝无理独发。然其发则气为之主也。
高峰以孟喜舜怒之类。为七情理发之證。而退溪先生答曰。是气之顺理而发。薰窃谓圣人之气。清明精粹。固无不善。则七情之发。虽由于气。而与发于理者。无以异也。若以七情中节之发。皆属之理。则其发于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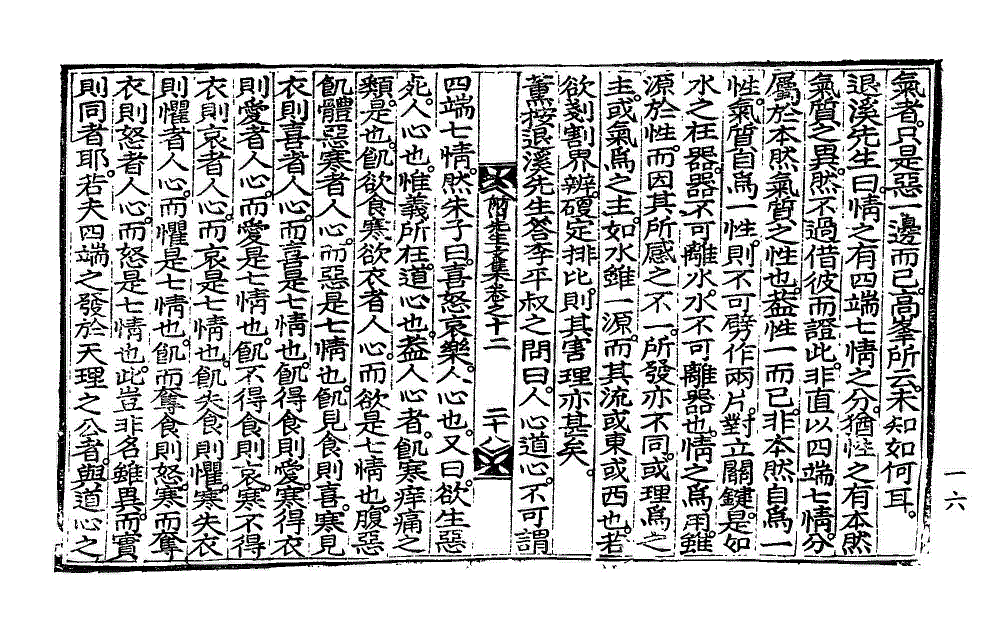 气者。只是恶一边而已。高峰所云。未知如何耳。
气者。只是恶一边而已。高峰所云。未知如何耳。退溪先生曰。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然气质之异。然不过借彼而證此。非直以四端七情。分属于本然气质之性也。盖性一而已。非本然自为一性。气质自为一性。则不可劈作两片。对立关键。是如水之在器。器不可离水。水不可离器也。情之为用。虽源于性。而因其所感之不一。所发亦不同。或理为之主。或气为之主。如水虽一源。而其流或东或西也。若欲刬割界辨。硬定排比。则其害理亦甚矣。
薰按退溪先生答李平叔之问曰。人心道心。不可谓四端七情。然朱子曰。喜怒哀乐。人心也。又曰。欲生恶死。人心也。惟义所在。道心也。盖人心者。饥寒痒痛之类。是也。饥欲食寒欲衣者人心。而欲是七情也。腹恶饥体恶寒者人心。而恶是七情也。饥见食则喜。寒见衣则喜者人心。而喜是七情也。饥得食则爱。寒得衣则爱者人心。而爱是七情也。饥不得食则哀。寒不得衣则哀者人心。而哀是七情也。饥失食则惧。寒失衣则惧者人心。而惧是七情也。饥而夺食则怒。寒而夺衣则怒者人心。而怒是七情也。此岂非名虽异。而实则同者耶。若夫四端之发于天理之公者。与道心之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7H 页
 原于性命之正者。固不可分而为二。退溪之意。以其人心道心。以心言。四端七情。以情言。当初命名之义。有些不同而云尔也。然究其根原来历。则不可谓不同。故答李宏仲之问曰。人心七情。道心四端也。盖心是理气之合。而未感物之时。寂然不动。一性浑然。及其感而遂通之际。仁义礼智之发。微妙而难见者。此道心也四端也。耳目口鼻之欲。危殆而易差者。此人心也七情也。故从古圣贤相对说下。而罗整庵以朱子或原或生之论。谓心有二歧之病。倡为人心道心体用之说。以为至静之体不可见。故曰微。至变之用不可测。故曰危。退溪斥之曰。夫限道心于未发之前。则道心是无与于叙秩命讨。而性为有体无用。判人心于已发之后。则是人心不资于本原性命。而情若有恶无善。如是则所谓不可见之微。不可测之危。二者之间。隔断横决。其视朱子说之该贯无遗。为如何哉。此固辨覈精详。无复疑晦。而栗谷所见。则与整庵不甚相远。以其说为高明超卓。而有欠于大本。仍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之论。不欲对待为说。以避二歧之嫌。至四端七情。则又与人心道心。同一议论。谓道心发现于人心之上。四端包在于七情之中。而七情
原于性命之正者。固不可分而为二。退溪之意。以其人心道心。以心言。四端七情。以情言。当初命名之义。有些不同而云尔也。然究其根原来历。则不可谓不同。故答李宏仲之问曰。人心七情。道心四端也。盖心是理气之合。而未感物之时。寂然不动。一性浑然。及其感而遂通之际。仁义礼智之发。微妙而难见者。此道心也四端也。耳目口鼻之欲。危殆而易差者。此人心也七情也。故从古圣贤相对说下。而罗整庵以朱子或原或生之论。谓心有二歧之病。倡为人心道心体用之说。以为至静之体不可见。故曰微。至变之用不可测。故曰危。退溪斥之曰。夫限道心于未发之前。则道心是无与于叙秩命讨。而性为有体无用。判人心于已发之后。则是人心不资于本原性命。而情若有恶无善。如是则所谓不可见之微。不可测之危。二者之间。隔断横决。其视朱子说之该贯无遗。为如何哉。此固辨覈精详。无复疑晦。而栗谷所见。则与整庵不甚相远。以其说为高明超卓。而有欠于大本。仍为人心道心。相为始终之论。不欲对待为说。以避二歧之嫌。至四端七情。则又与人心道心。同一议论。谓道心发现于人心之上。四端包在于七情之中。而七情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7L 页
 之外。更无所谓四端。张皇持论。乐浑沦而厌分析。其归宿则只有气发一途。理是窈冥枯槁无用一死物。退溪所谓限道心于未发之前者。岂独中整庵之病而已哉。
之外。更无所谓四端。张皇持论。乐浑沦而厌分析。其归宿则只有气发一途。理是窈冥枯槁无用一死物。退溪所谓限道心于未发之前者。岂独中整庵之病而已哉。栗谷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盖栗谷主张气字。太过。遗却理发一款。自作定论。而谓以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然孔子之一贯。孟子之四端。皆就人心上。拈出。是理之流行发见也。朱子云。太极之动静。是理之动静。则理何尝无为而不能自发耶。
栗谷曰。所谓气发而理乘。非但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薰窃谓见之而恻隐。虽似乎气。而所谓恻隐。素具于吾心。随所见而直发。是乃仁之端也。仁端之直发者。谓之理发可乎。谓之气发可乎。若谓之气发。则是认仁为气矣。岂特名言之差而已哉。
栗谷曰。气发而理乘者。阴静阳动。而机自尔也。非有使之者也。又曰。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原其未然而言也。动静者。所乘之机。见其已然而言也。薰窃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8H 页
 谓栗谷以理无为。气有为之。故而其言如此。然理乃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不是虚无空寂底物。则凡化生发育。三光迭运。万物咸遂。夏热冬寒。山峙水流。桃红李白。马鬣牛角。亘万古如一日者。皆理之所为也。若一任阴阳气化之为。而理不得为主。则其将夏寒冬热。山夷川涌。桃生李花。马生牛角。天地不成其为天地。万物不成其为万物。诡异差忒。何可胜言也哉。
谓栗谷以理无为。气有为之。故而其言如此。然理乃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不是虚无空寂底物。则凡化生发育。三光迭运。万物咸遂。夏热冬寒。山峙水流。桃红李白。马鬣牛角。亘万古如一日者。皆理之所为也。若一任阴阳气化之为。而理不得为主。则其将夏寒冬热。山夷川涌。桃生李花。马生牛角。天地不成其为天地。万物不成其为万物。诡异差忒。何可胜言也哉。退溪先生以人马。喻理气之互发曰。人马相须不相离。或指言人行。则不须并言马。而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马行。则不须并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情是也。此置水不漏之论也。栗谷曰。或有马从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乃人心也。其曰马从人意者。非气随理之谓乎。其曰人信马足者。非理乘气之谓乎。以此验之。亦可见理气之互发。而反斥退溪之言何耶。且人信马之喻。细究之则不为无病。人只信马足而行。不失轨途者几希。设或马不奔骤。不失轨途。是偶然与人意合。非良御之所为也。夫易危者人心。故道心常管摄。然后人心不为驰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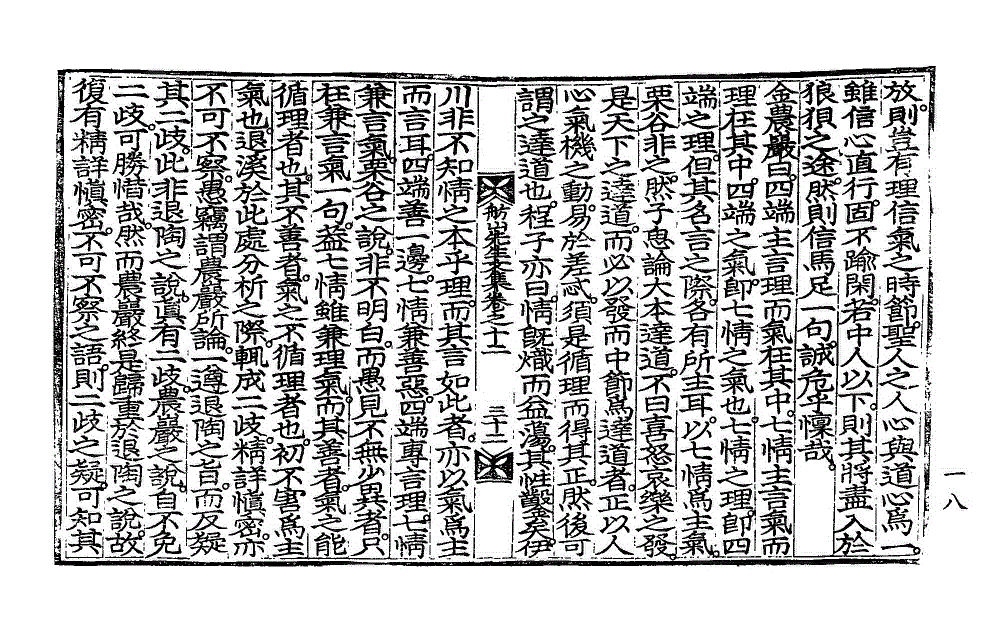 放。则岂有理信气之时节。圣人之人心与道心为一。虽信心直行。固不踰闲。若中人以下。则其将尽入于狼狈之途。然则信马足一句。诚危乎懔哉。
放。则岂有理信气之时节。圣人之人心与道心为一。虽信心直行。固不踰闲。若中人以下。则其将尽入于狼狈之途。然则信马足一句。诚危乎懔哉。金农岩曰。四端主言理而气在其中。七情主言气而理在其中。四端之气。即七情之气也。七情之理。即四端之理。但其名言之际。各有所主耳。以七情为主气。栗谷非之。然子思论大本达道。不曰喜怒哀乐之发。是天下之达道。而必以发而中节为达道者。正以人心气机之动。易于差忒。须是循理而得其正。然后可谓之达道也。程子亦曰。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伊川非不知情之本乎理。而其言如此者。亦以气为主而言耳。四端善一边。七情兼善恶。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栗谷之说。非不明白。而愚见不无少异者。只在兼言气一句。盖七情虽兼理气。而其善者。气之能循理者也。其不善者。气之不循理者也。初不害为主气也。退溪于此处分析之际。辄成二歧。精详慎密。亦不可不察。愚窃谓农岩所论。一遵退陶之旨。而反疑其二歧。此非退陶之说。真有二歧。农岩之说。自不免二歧。可胜惜哉。然而农岩终是归重于退陶之说。故复有精详慎密。不可不察之语。则二歧之疑。可知其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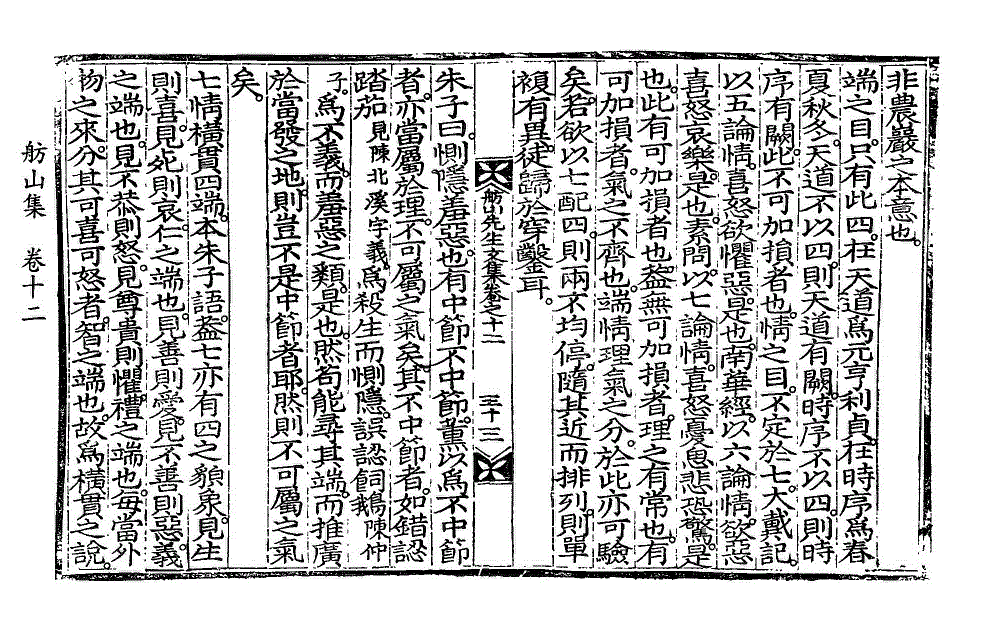 非农岩之本意也。
非农岩之本意也。端之目。只有此四。在天道为元亨利贞。在时序为春夏秋冬。天道不以四。则天道有阙。时序不以四。则时序有阙。此不可加损者也。情之目。不定于七。大戴记。以五论情。喜怒欲惧恶。是也。南华经。以六论情。欲恶喜怒哀乐。是也。素问。以七论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此有可加损者也。盖无可加损者。理之有常也。有可加损者。气之不齐也。端情理气之分。于此亦可验矣。若欲以七配四。则两不均停。随其近而排列。则单复有异。徒归于穿凿耳。
朱子曰。恻隐羞恶。也有中节不中节。薰以为不中节者。亦当属于理。不可属之气矣。其不中节者。如错认踏茄(见陈北溪字义。)为杀生而恻隐。误认饲鹅(陈仲子。)为不义。而羞恶之类。是也。然苟能寻其端。而推广于当发之地。则岂不是中节者耶。然则不可属之气矣。
七情横贯四端。本朱子语。盖七亦有四之貌象。见生则喜。见死则哀。仁之端也。见善则爱。见不善则恶。义之端也。见不恭则怒。见尊贵则惧。礼之端也。每当外物之来。分其可喜可怒者。智之端也。故为横贯之说。
舫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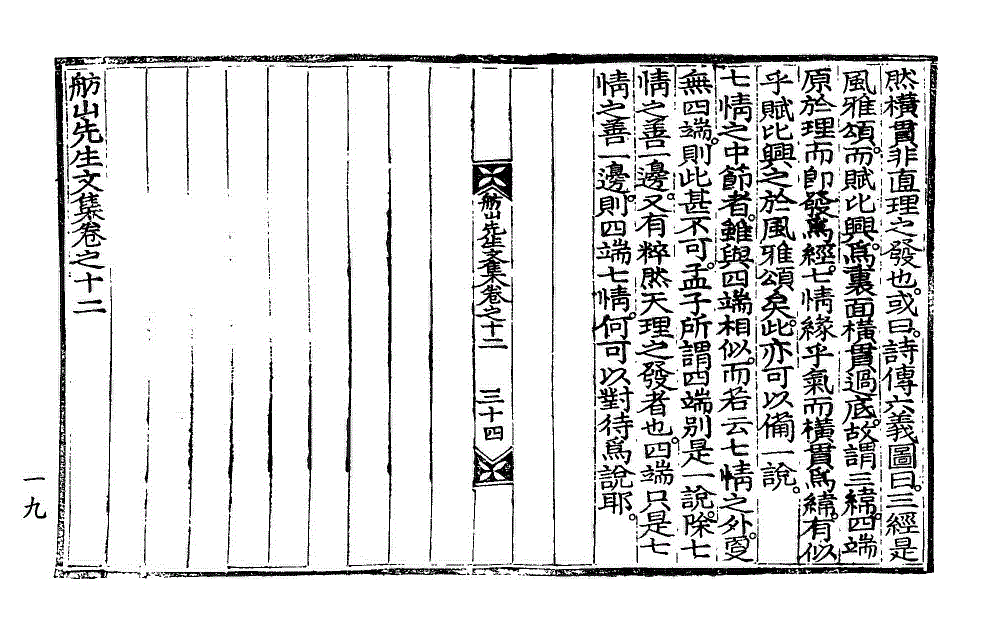 然横贯非直理之发也。或曰。诗传六义图曰。三经是风雅颂。而赋比兴。为里面横贯过底。故谓三纬。四端原于理而即发为经。七情缘乎气而横贯为纬。有似乎赋比兴之于风雅颂矣。此亦可以备一说。
然横贯非直理之发也。或曰。诗传六义图曰。三经是风雅颂。而赋比兴。为里面横贯过底。故谓三纬。四端原于理而即发为经。七情缘乎气而横贯为纬。有似乎赋比兴之于风雅颂矣。此亦可以备一说。七情之中节者。虽与四端相似。而若云七情之外。更无四端。则此甚不可。孟子所谓四端别是一说。除七情之善一边。又有粹然天理之发者也。四端只是七情之善一边。则四端七情。何可以对待为说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