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x 页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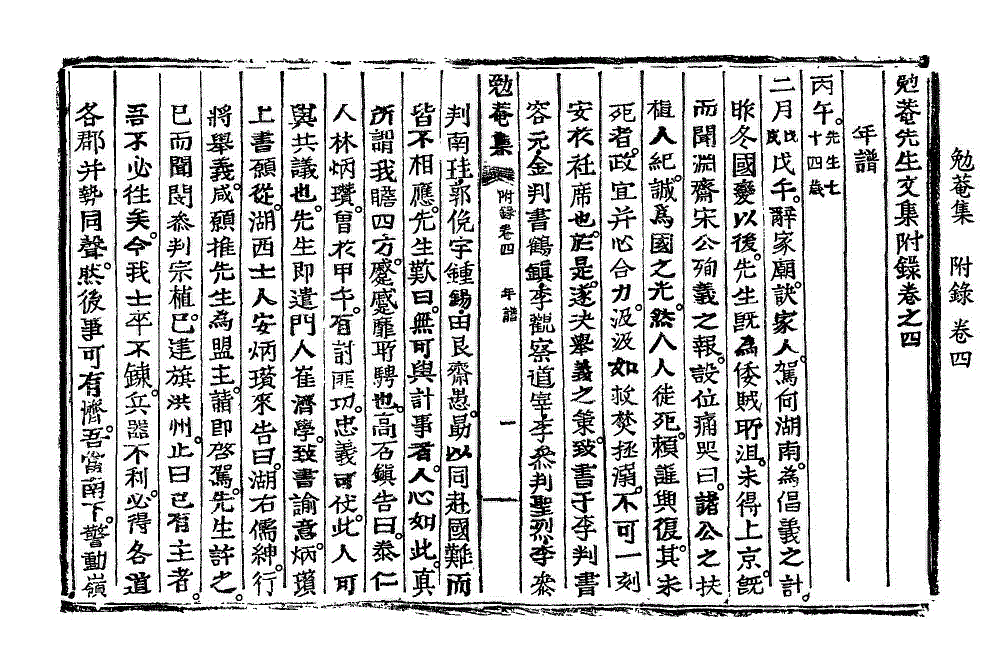 年谱
年谱丙午。(先生七十四岁。)
二月(戊戌)戊午。辞家庙。诀家人。驾向湖南。为倡义之计。
昨冬国变以后。先生既为倭贼所沮。未得上京。既而闻渊斋宋公殉义之报。设位痛哭曰。诸公之扶植人纪。诚为国之光。然人人徒死。赖谁兴复。其未死者。政宜并心合力。汲汲如救焚拯溺。不可一刻安于衽席也。于是。遂决举义之策。致书于李判书容元,金判书鹤镇,李观察道宰,李参判圣烈,李参判南圭,郭俛宇钟锡,田艮斋愚。勖以同赴国难而皆不相应。先生叹曰。无可与计事者。人心如此。真所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也。高石镇告曰。泰仁人林炳瓒。曾于甲午。有讨匪切。忠义可仗。此人可与共议也。先生即遣门人崔济学。致书谕意。炳瓒上书愿从。湖西士人安炳瓒来告曰。湖右儒绅。行将举义。咸愿推先生为盟主。请即启驾。先生许之。已而闻闵参判宗植。已建旗洪州。止曰已有主者。吾不必往矣。今我士卒不鍊。兵器不利。必得各道各郡并势同声。然后事可有济。吾当南下。警动岭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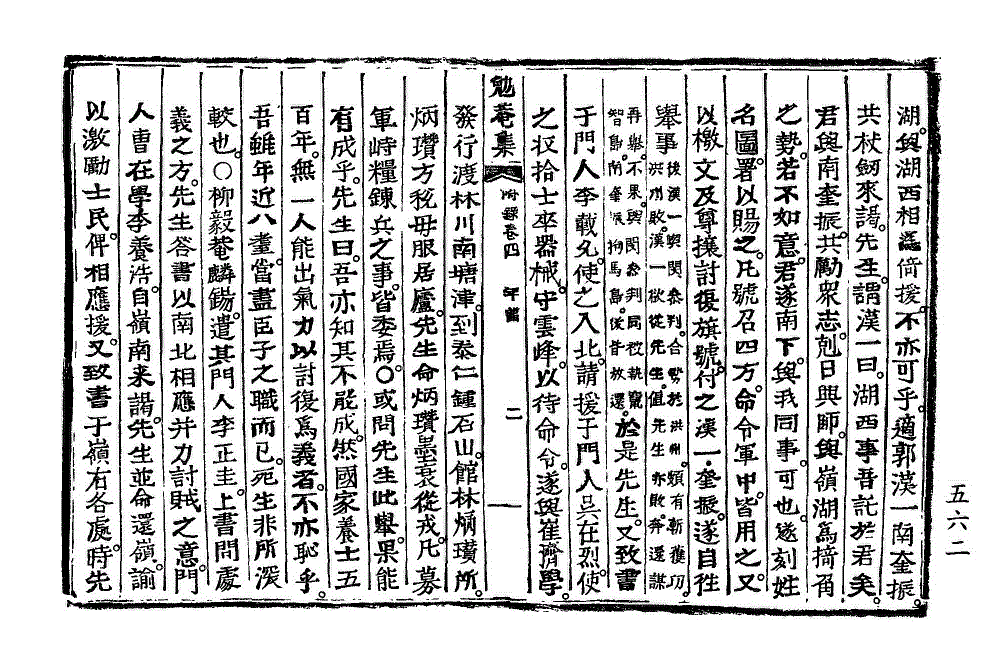 湖。与湖西相为倚援。不亦可乎。适郭汉一南奎振。共杖剑来谒。先生。谓汉一曰。湖西事吾托于君矣。君与南奎振。共励众志。剋日兴师。与岭湖为掎角之势。若不如意。君遂南下。与我同事。可也。遂刻姓名图。署以赐之。凡号召四方。命令军中。皆用之。又以檄文及尊攘讨复旗号。付之汉一,奎振。遂自往举事(后汉一与闵参判。合势于洪州。颇有斩获功。洪州败。汉一欲从先生。值先生亦败。奔还谋再举。不果。与闵参判同被执窜智岛。南奎振拘马岛。后皆放还。)于是先生。又致书于门人李载允。使之入北。请援于门人吴在烈。使之收拾士卒器械。守云峰。以待命令。遂与崔济学。发行渡林川南塘津。到泰仁钟石山。馆林炳瓒所。炳瓒方税母服居庐。先生命炳瓒墨衰从戎。凡募军峙粮鍊兵之事。皆委焉。○或问先生此举。果能有成乎。先生曰。吾亦知其不能成。然国家养士五百年。无一人能出气力以讨复为义者。不亦耻乎。吾虽年近八耋。当尽臣子之职而已。死生非所深较也。○柳毅庵麟锡。遣其门人李正圭。上书问处义之方。先生答书以南北相应并力讨贼之意。门人曹在学,李养浩。自岭南来谒。先生并命还岭。谕以激励士民。俾相应援。又致书于岭右各处。时先
湖。与湖西相为倚援。不亦可乎。适郭汉一南奎振。共杖剑来谒。先生。谓汉一曰。湖西事吾托于君矣。君与南奎振。共励众志。剋日兴师。与岭湖为掎角之势。若不如意。君遂南下。与我同事。可也。遂刻姓名图。署以赐之。凡号召四方。命令军中。皆用之。又以檄文及尊攘讨复旗号。付之汉一,奎振。遂自往举事(后汉一与闵参判。合势于洪州。颇有斩获功。洪州败。汉一欲从先生。值先生亦败。奔还谋再举。不果。与闵参判同被执窜智岛。南奎振拘马岛。后皆放还。)于是先生。又致书于门人李载允。使之入北。请援于门人吴在烈。使之收拾士卒器械。守云峰。以待命令。遂与崔济学。发行渡林川南塘津。到泰仁钟石山。馆林炳瓒所。炳瓒方税母服居庐。先生命炳瓒墨衰从戎。凡募军峙粮鍊兵之事。皆委焉。○或问先生此举。果能有成乎。先生曰。吾亦知其不能成。然国家养士五百年。无一人能出气力以讨复为义者。不亦耻乎。吾虽年近八耋。当尽臣子之职而已。死生非所深较也。○柳毅庵麟锡。遣其门人李正圭。上书问处义之方。先生答书以南北相应并力讨贼之意。门人曹在学,李养浩。自岭南来谒。先生并命还岭。谕以激励士民。俾相应援。又致书于岭右各处。时先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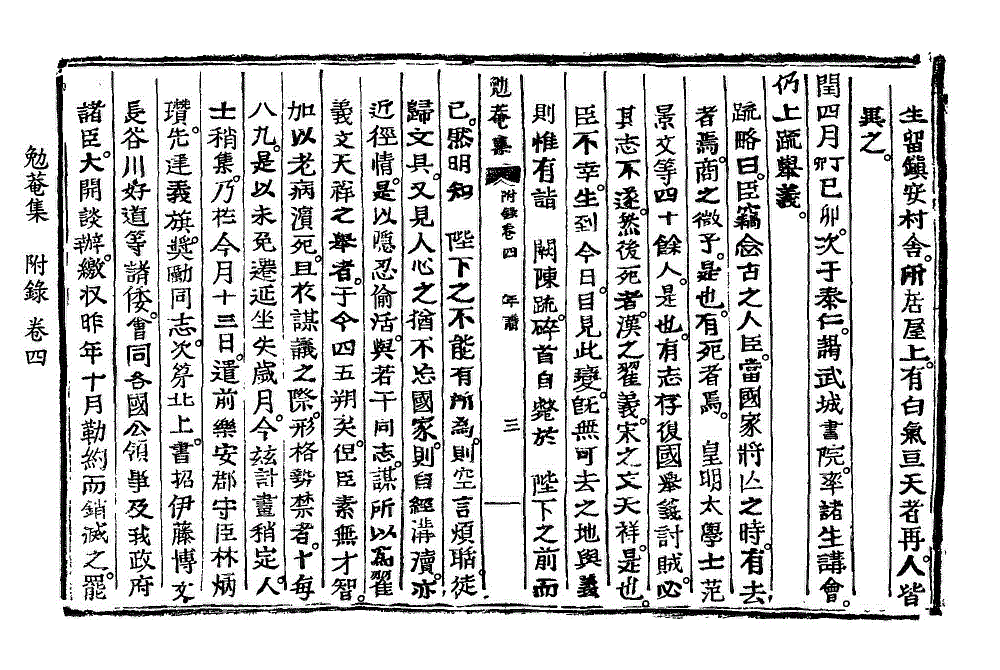 生留镇安村舍。所居屋上。有白气亘天者再。人皆异之。
生留镇安村舍。所居屋上。有白气亘天者再。人皆异之。闰四月(丁卯)己卯。次于泰仁。谒武城书院。率诸生讲会。仍上疏举义。
疏略曰。臣窃念古之人臣。当国家将亡之时。有去者焉。商之微子。是也。有死者焉。 皇明太学士范景文等四十馀人。是也。有志存复国举义讨贼。必其志不遂。然后死者。汉之翟义。宋之文天祥。是也。臣不幸。生到今日。目见此变。既无可去之地与义则惟有诣 阙陈疏。碎首自毙于 陛下之前而已。然明知 陛下之不能有所为。则空言烦聒。徒归文具。又见人心之犹不忘国家。则自经沟渎。亦近径情。是以隐忍偷活。与若干同志。谋所以为翟义文天祥之举者。于今四五朔矣。但臣素无才智。加以老病滨死。且于谋议之际。形格势禁者。十每八九。是以未免迁延坐失岁月。今玆计画稍定。人士稍集。乃于今月十三日。遣前乐安郡守臣林炳瓒。先建义旗。奖励同志。次第北上。书招伊藤博文,长谷川,好道等诸倭。会同各国公领事及我政府诸臣。大开谈办。缴收昨年十月勒约而销灭之。罢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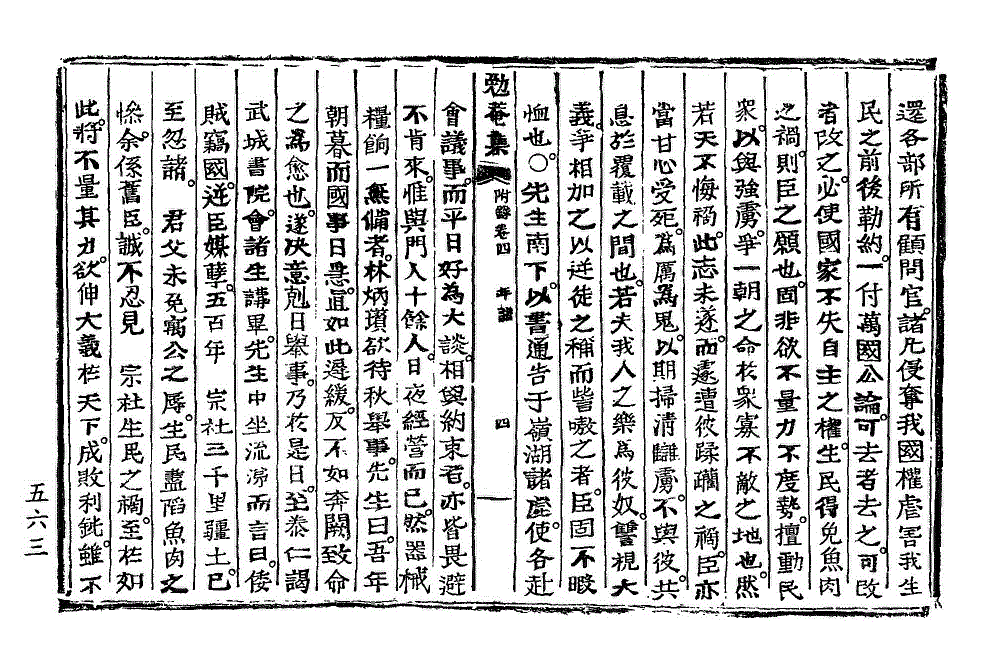 还各部所有顾问官。诸凡侵夺我国权虐害我生民之前后勒约。一付万国公论。可去者去之。可改者改之。必使国家不失自主之权。生民得免鱼肉之祸。则臣之愿也。固非欲不量力不度势。擅动民众。以与强虏。争一朝之命于众寡不敌之地也。然若天不悔𥚁。此志未遂。而遽遭彼蹂躏之𥚁。臣亦当甘心受死。为厉为鬼。以期扫清雠虏。不与彼。共息于覆载之间也。若夫我人之乐为彼奴。雠视大义。争相加之以逆徒之称而訾嗷之者。臣固不暇恤也。○先生南下。以书通告于岭湖诸处。使各赴会议事。而平日好为大谈。相与约束者。亦皆畏避不肯来。惟与门人十馀人。日夜经营而已。然器械粮饷一无备者。林炳瓒欲待秋举事。先生曰。吾年朝暮而国事日急。直如此迟缓。反不如奔阙致命之为愈也。遂决意剋日举事。乃于是日。至泰仁谒武城书院。会诸生讲毕。先生中坐流涕而言曰。倭贼窃国。逆臣媒孽。五百年 宗社三千里疆土。已至忽诸。 君父未免寓公之辱。生民尽陷鱼肉之惨。余系旧臣。诚不忍见 宗社生民之𥚁。至于如此。将不量其力。欲伸大义于天下。成败利钝。虽不
还各部所有顾问官。诸凡侵夺我国权虐害我生民之前后勒约。一付万国公论。可去者去之。可改者改之。必使国家不失自主之权。生民得免鱼肉之祸。则臣之愿也。固非欲不量力不度势。擅动民众。以与强虏。争一朝之命于众寡不敌之地也。然若天不悔𥚁。此志未遂。而遽遭彼蹂躏之𥚁。臣亦当甘心受死。为厉为鬼。以期扫清雠虏。不与彼。共息于覆载之间也。若夫我人之乐为彼奴。雠视大义。争相加之以逆徒之称而訾嗷之者。臣固不暇恤也。○先生南下。以书通告于岭湖诸处。使各赴会议事。而平日好为大谈。相与约束者。亦皆畏避不肯来。惟与门人十馀人。日夜经营而已。然器械粮饷一无备者。林炳瓒欲待秋举事。先生曰。吾年朝暮而国事日急。直如此迟缓。反不如奔阙致命之为愈也。遂决意剋日举事。乃于是日。至泰仁谒武城书院。会诸生讲毕。先生中坐流涕而言曰。倭贼窃国。逆臣媒孽。五百年 宗社三千里疆土。已至忽诸。 君父未免寓公之辱。生民尽陷鱼肉之惨。余系旧臣。诚不忍见 宗社生民之𥚁。至于如此。将不量其力。欲伸大义于天下。成败利钝。虽不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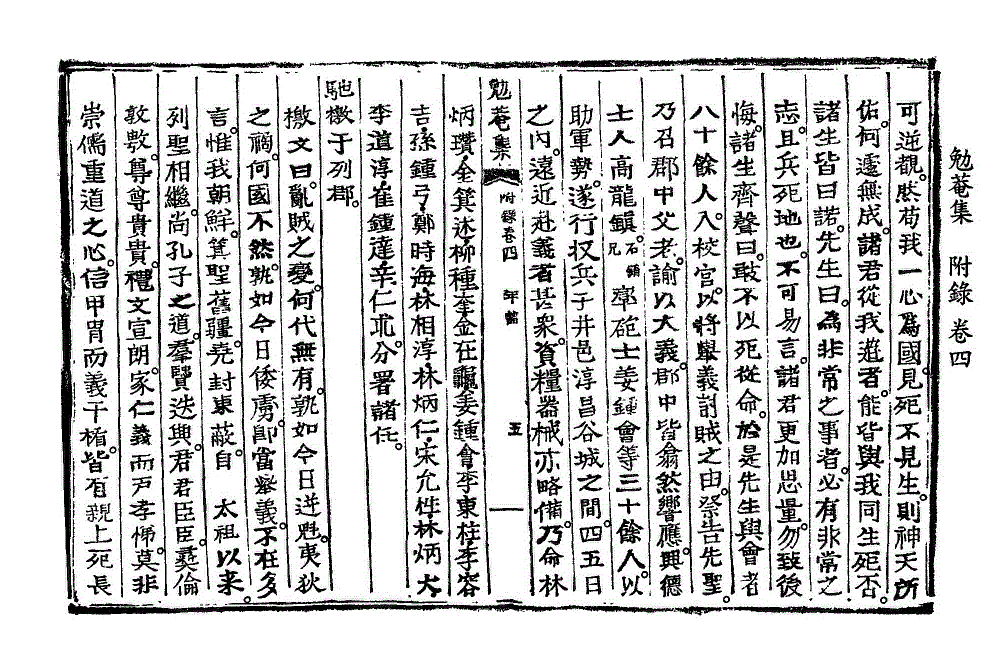 可逆睹。然苟我一心为国。见死不见生。则神天所佑。何遽无成。诸君从我游者。能皆与我同生死否。诸生皆曰诺。先生曰。为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志。且兵死地也。不可易言。诸君更加思量。勿致后悔。诸生齐声曰。敢不以死从命。于是先生与会者八十馀人。入校宫。以将举义讨贼之由。祭告先圣。乃召郡中父老。谕以大义。郡中皆翕然响应。兴德士人高龙镇。(石镇兄)率炮士姜钟会等三十馀人。以助军势。遂行收兵于井邑淳昌谷城之间。四五日之内。远近赴义者甚众。资粮器械亦略备。乃命林炳瓒,金箕述,柳种奎,金在龟,姜钟会,李东柱,李容吉,孙钟弓,郑时海,林相淳,林炳仁,宋允性,林炳大,李道淳,崔钟达,辛仁求。分署诸任。
可逆睹。然苟我一心为国。见死不见生。则神天所佑。何遽无成。诸君从我游者。能皆与我同生死否。诸生皆曰诺。先生曰。为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志。且兵死地也。不可易言。诸君更加思量。勿致后悔。诸生齐声曰。敢不以死从命。于是先生与会者八十馀人。入校宫。以将举义讨贼之由。祭告先圣。乃召郡中父老。谕以大义。郡中皆翕然响应。兴德士人高龙镇。(石镇兄)率炮士姜钟会等三十馀人。以助军势。遂行收兵于井邑淳昌谷城之间。四五日之内。远近赴义者甚众。资粮器械亦略备。乃命林炳瓒,金箕述,柳种奎,金在龟,姜钟会,李东柱,李容吉,孙钟弓,郑时海,林相淳,林炳仁,宋允性,林炳大,李道淳,崔钟达,辛仁求。分署诸任。驰檄于列郡。
檄文曰。乱贼之变。何代无有。孰如今日逆魁。夷狄之𥚁。何国不然。孰如今日倭虏。即当举义。不在多言。惟我朝鲜。箕圣旧疆。尧封东蔽。自 太祖以来。列圣相继。尚孔子之道。群贤迭兴。君君臣臣。彝伦敦敷。尊尊贵贵。礼文宣朗。家仁义而户孝悌。莫非崇儒重道之心。信甲冑而义干楯。皆有亲上死长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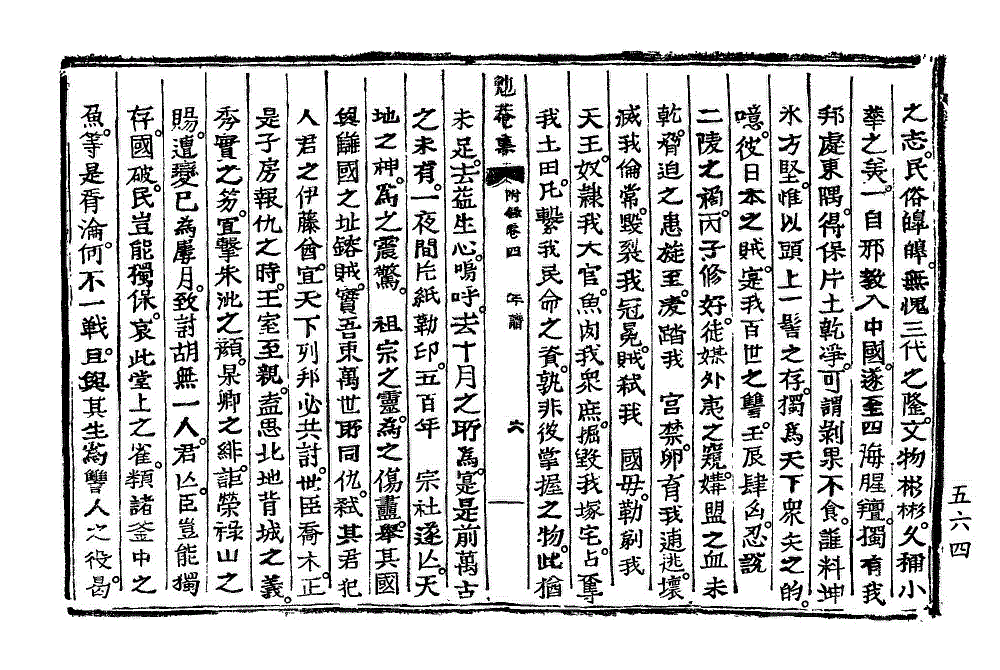 之志。民俗皞皞。无愧三代之隆。文物彬彬。久称小华之美。一自邪教入中国。遂至四海腥膻。独有我邦处东隅。得保片土乾净。可谓剥果不食。谁料坤冰方坚。惟以头上一髻之存。独为天下众矢之的。噫。彼日本之贼。寔我百世之雠。壬辰肆凶。忍说 二陵之𥚁。丙子修好。徒媒外夷之窥。媾盟之血未乾。胁迫之患旋至。凌踏我 宫禁。卵育我逋逃。坏灭我伦常。毁裂我冠冕。贼弑我 国母。勒剃我 天王。奴隶我大官。鱼肉我众庶。掘毁我冢宅。占夺我土田。凡系我民命之资。孰非彼掌握之物。此犹未足。去益生心。呜呼。去十月之所为。寔是前万古之未有。一夜间片纸勒印。五百年 宗社遂亡。天地之神。为之震惊。 祖宗之灵。为之伤衋。举其国与雠国之址镕贼。实吾东万世所同仇。弑其君犯人君之伊藤酋。宜天下列邦必共讨。世臣乔木。正是子房报仇之时。王室至亲。盍思北地背城之义。秀实之笏。宜击朱泚之颜。杲卿之绯。讵荣禄山之赐。遭变已为屡月。致讨胡无一人。君亡。臣岂能独存。国破。民岂能独保。哀此堂上之雀。类诸釜中之鱼。等是胥沦。何不一战。且与其生为雠人之役。曷
之志。民俗皞皞。无愧三代之隆。文物彬彬。久称小华之美。一自邪教入中国。遂至四海腥膻。独有我邦处东隅。得保片土乾净。可谓剥果不食。谁料坤冰方坚。惟以头上一髻之存。独为天下众矢之的。噫。彼日本之贼。寔我百世之雠。壬辰肆凶。忍说 二陵之𥚁。丙子修好。徒媒外夷之窥。媾盟之血未乾。胁迫之患旋至。凌踏我 宫禁。卵育我逋逃。坏灭我伦常。毁裂我冠冕。贼弑我 国母。勒剃我 天王。奴隶我大官。鱼肉我众庶。掘毁我冢宅。占夺我土田。凡系我民命之资。孰非彼掌握之物。此犹未足。去益生心。呜呼。去十月之所为。寔是前万古之未有。一夜间片纸勒印。五百年 宗社遂亡。天地之神。为之震惊。 祖宗之灵。为之伤衋。举其国与雠国之址镕贼。实吾东万世所同仇。弑其君犯人君之伊藤酋。宜天下列邦必共讨。世臣乔木。正是子房报仇之时。王室至亲。盍思北地背城之义。秀实之笏。宜击朱泚之颜。杲卿之绯。讵荣禄山之赐。遭变已为屡月。致讨胡无一人。君亡。臣岂能独存。国破。民岂能独保。哀此堂上之雀。类诸釜中之鱼。等是胥沦。何不一战。且与其生为雠人之役。曷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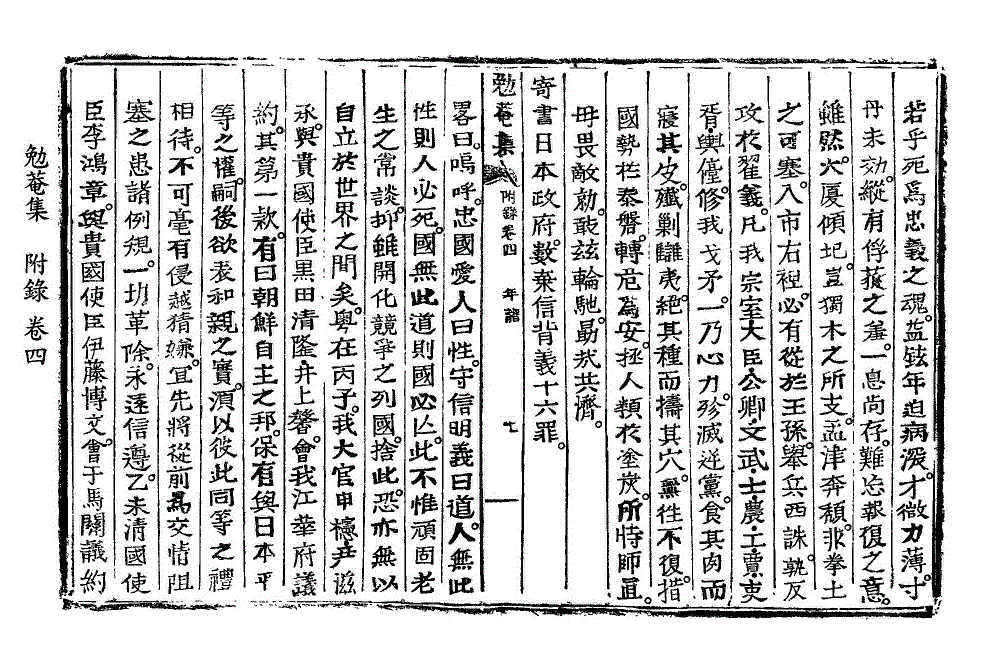 若乎死为忠义之魂。益铉年迫病深。才微力薄。寸丹未效。纵有俘获之羞。一息尚存。难忘报复之意。虽然。大厦倾圮。岂独木之所支。孟津奔颓。非拳土之可塞。入市右袒。必有从于王孙。举兵西诛。孰反攻于翟义。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农,工,贾,吏胥,舆儓。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灭逆党。食其肉而寝其皮。歼剿雠夷。绝其种而捣其穴。无往不复。措国势于泰磐。转危为安。拯人类于涂炭。所恃师直。毋畏敌勍。敢玆轮驰。勖哉共济。
若乎死为忠义之魂。益铉年迫病深。才微力薄。寸丹未效。纵有俘获之羞。一息尚存。难忘报复之意。虽然。大厦倾圮。岂独木之所支。孟津奔颓。非拳土之可塞。入市右袒。必有从于王孙。举兵西诛。孰反攻于翟义。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农,工,贾,吏胥,舆儓。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灭逆党。食其肉而寝其皮。歼剿雠夷。绝其种而捣其穴。无往不复。措国势于泰磐。转危为安。拯人类于涂炭。所恃师直。毋畏敌勍。敢玆轮驰。勖哉共济。寄书日本政府。数弃信背义十六罪。
略曰。呜呼。忠国爱人曰性。守信明义曰道。人无此性则人必死。国无此道则国必亡。此不惟顽固老生之常谈。抑虽开化竞争之列国。舍此。恐亦无以自立于世界之间矣。粤在丙子。我大官申櫶,尹滋承。与贵国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会我江华府议约。其第一款。有曰朝鲜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嗣后欲表和亲之实。须以彼此同等之礼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宜先将从前为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除。永远信遵。乙未清国使臣李鸿章。与贵国使臣伊藤博文。会于马关议约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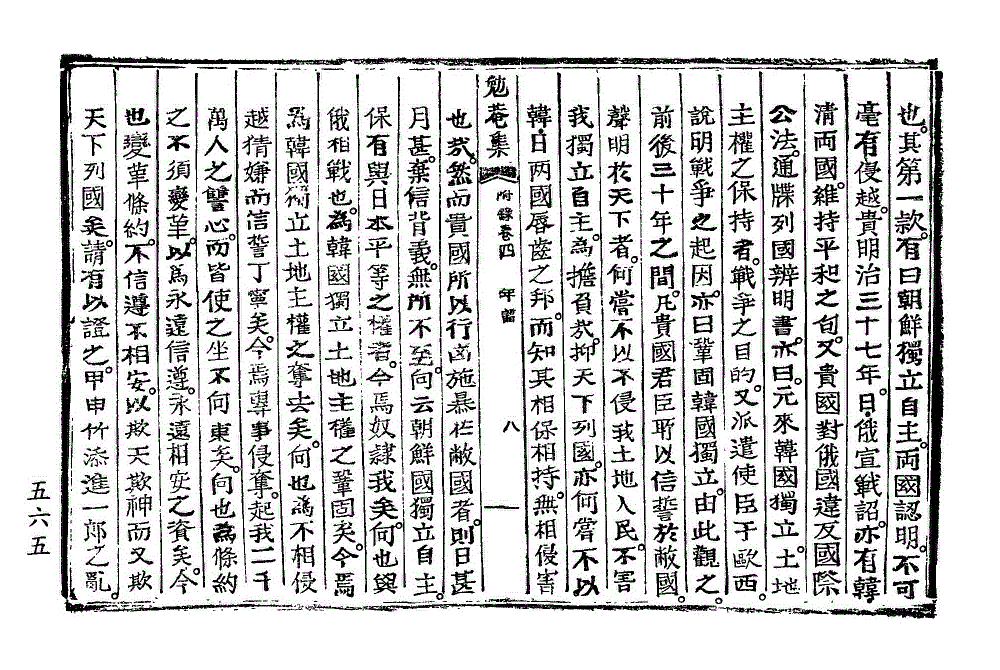 也。其第一款。有曰朝鲜独立自主。两国认明。不可毫有侵越。贵明治三十七年。日,俄宣战诏。亦有韩,清两国。维持平和之句。又贵国对俄国违反国际公法。通牒列国辨明书。亦曰。元来韩国独立。土地主权之保持者。战争之目的。又派遣使臣于欧西。说明战争之起因。亦曰巩固韩国独立。由此观之。前后三十年之间。凡贵国君臣所以信誓于敝国。声明于天下者。何尝不以不侵我土地人民。不害我独立自主。为担负哉。抑天下列国。亦何尝不以韩,日两国唇齿之邦。而知其相保相持。无相侵害也哉。然而贵国所以行凶施暴于敝国者。则日甚月甚。弃信背义。无所不至。向云朝鲜国独立自主。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者。今焉奴隶我矣。向也与俄相战也。为韩国独立土地主权之巩固矣。今焉为韩国独立土地主权之夺去矣。向也为不相侵越猜嫌而信誓丁宁矣。今焉专事侵夺。起我二千万人之雠心。而皆使之坐不向东矣。向也为条约之不须变革。以为永远信遵。永远相安之资矣。今也变革条约。不信遵不相安。以欺天欺神而又欺天下列国矣。请有以證之。甲申竹添进一郎之乱。
也。其第一款。有曰朝鲜独立自主。两国认明。不可毫有侵越。贵明治三十七年。日,俄宣战诏。亦有韩,清两国。维持平和之句。又贵国对俄国违反国际公法。通牒列国辨明书。亦曰。元来韩国独立。土地主权之保持者。战争之目的。又派遣使臣于欧西。说明战争之起因。亦曰巩固韩国独立。由此观之。前后三十年之间。凡贵国君臣所以信誓于敝国。声明于天下者。何尝不以不侵我土地人民。不害我独立自主。为担负哉。抑天下列国。亦何尝不以韩,日两国唇齿之邦。而知其相保相持。无相侵害也哉。然而贵国所以行凶施暴于敝国者。则日甚月甚。弃信背义。无所不至。向云朝鲜国独立自主。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者。今焉奴隶我矣。向也与俄相战也。为韩国独立土地主权之巩固矣。今焉为韩国独立土地主权之夺去矣。向也为不相侵越猜嫌而信誓丁宁矣。今焉专事侵夺。起我二千万人之雠心。而皆使之坐不向东矣。向也为条约之不须变革。以为永远信遵。永远相安之资矣。今也变革条约。不信遵不相安。以欺天欺神而又欺天下列国矣。请有以證之。甲申竹添进一郎之乱。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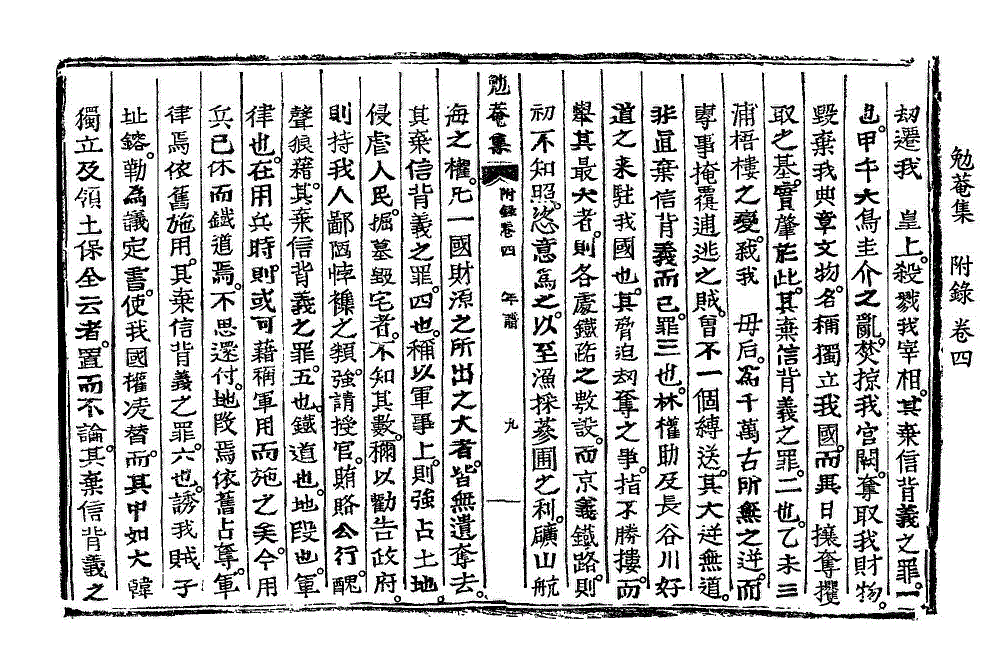 劫迁我 皇上。杀戮我宰相。其弃信背义之罪。一也。甲午大鸟圭介之乱。焚掠我宫阙。夺取我财物。毁弃我典章文物。名称独立我国。而异日攘夺攫取之基。实肇于此。其弃信背义之罪。二也。乙未三浦梧楼之变。弑我 母后。为千万古所无之逆。而专事掩覆逋逃之贼。曾不一个缚送。其大逆无道。非直弃信背义而已。罪三也。林权助及长谷川好道之来驻我国也。其胁迫劫夺之事。指不胜搂。而举其最大者。则各处铁路之敷设。而京义铁路。则初不知照。恣意为之。以至渔采蔘圃之利。矿山航海之权。凡一国财源之所出之大者。皆无遗夺去。其弃信背义之罪。四也。称以军事上。则强占土地。侵虐人民。掘墓毁宅者。不知其数。称以劝告政府。则持我人鄙陋悖杂之类。强请授官。贿赂公行。丑声狼藉。其弃信背义之罪。五也。铁道也。地段也。军律也。在用兵时。则或可藉称军用而施之矣。今用兵已休而铁道焉。不思还付。地段焉依旧占夺。军律焉依旧施用。其弃信背义之罪。六也。诱我贼子址镕。勒为议定书。使我国权凌替。而其中如大韩独立及领土保全云者。置而不论。其弃信背义之
劫迁我 皇上。杀戮我宰相。其弃信背义之罪。一也。甲午大鸟圭介之乱。焚掠我宫阙。夺取我财物。毁弃我典章文物。名称独立我国。而异日攘夺攫取之基。实肇于此。其弃信背义之罪。二也。乙未三浦梧楼之变。弑我 母后。为千万古所无之逆。而专事掩覆逋逃之贼。曾不一个缚送。其大逆无道。非直弃信背义而已。罪三也。林权助及长谷川好道之来驻我国也。其胁迫劫夺之事。指不胜搂。而举其最大者。则各处铁路之敷设。而京义铁路。则初不知照。恣意为之。以至渔采蔘圃之利。矿山航海之权。凡一国财源之所出之大者。皆无遗夺去。其弃信背义之罪。四也。称以军事上。则强占土地。侵虐人民。掘墓毁宅者。不知其数。称以劝告政府。则持我人鄙陋悖杂之类。强请授官。贿赂公行。丑声狼藉。其弃信背义之罪。五也。铁道也。地段也。军律也。在用兵时。则或可藉称军用而施之矣。今用兵已休而铁道焉。不思还付。地段焉依旧占夺。军律焉依旧施用。其弃信背义之罪。六也。诱我贼子址镕。勒为议定书。使我国权凌替。而其中如大韩独立及领土保全云者。置而不论。其弃信背义之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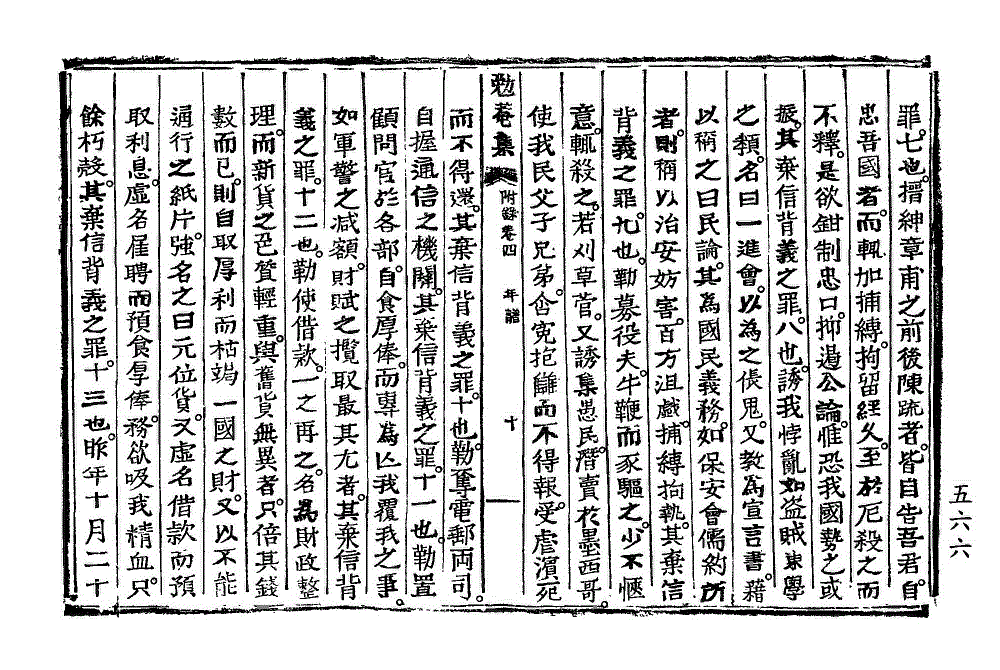 罪。七也。搢绅章甫之前后陈疏者。皆自告吾君。自忠吾国者。而辄加捕缚。拘留经久。至于厄杀之而不释。是欲钳制忠口。抑遏公论。惟恐我国势之或振。其弃信背义之罪。八也。诱我悖乱如盗贼东学之类。名曰一进会。以为之伥鬼。又教为宣言书。藉以称之曰民论。其为国民义务。如保安会儒约所者。则称以治安妨害。百方沮戏。捕缚拘执。其弃信背义之罪。九也。勒募役夫。牛鞭而豕驱之。少不惬意。辄杀之。若刈草菅。又诱集愚民。潜卖于墨西哥。使我民父子兄弟。含冤抱雠而不得报。受虐滨死而不得还。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也。勒夺电邮两司。自握通信之机关。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一也。勒置顾问官于各部。自食厚俸。而专为亡我覆我之事。如军警之减额。财赋之揽取最其尤者。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二也。勒使借款。一之再之。名为财政整理。而新货之色质轻重。与旧货无异者。只倍其钱数而已。则自取厚利而枯竭一国之财。又以不能通行之纸片。强名之曰元位货。又虚名借款而预取利息。虚名雇聘而预食厚俸。务欲吸我精血。只馀朽壳。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三也。昨年十月二十
罪。七也。搢绅章甫之前后陈疏者。皆自告吾君。自忠吾国者。而辄加捕缚。拘留经久。至于厄杀之而不释。是欲钳制忠口。抑遏公论。惟恐我国势之或振。其弃信背义之罪。八也。诱我悖乱如盗贼东学之类。名曰一进会。以为之伥鬼。又教为宣言书。藉以称之曰民论。其为国民义务。如保安会儒约所者。则称以治安妨害。百方沮戏。捕缚拘执。其弃信背义之罪。九也。勒募役夫。牛鞭而豕驱之。少不惬意。辄杀之。若刈草菅。又诱集愚民。潜卖于墨西哥。使我民父子兄弟。含冤抱雠而不得报。受虐滨死而不得还。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也。勒夺电邮两司。自握通信之机关。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一也。勒置顾问官于各部。自食厚俸。而专为亡我覆我之事。如军警之减额。财赋之揽取最其尤者。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二也。勒使借款。一之再之。名为财政整理。而新货之色质轻重。与旧货无异者。只倍其钱数而已。则自取厚利而枯竭一国之财。又以不能通行之纸片。强名之曰元位货。又虚名借款而预取利息。虚名雇聘而预食厚俸。务欲吸我精血。只馀朽壳。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三也。昨年十月二十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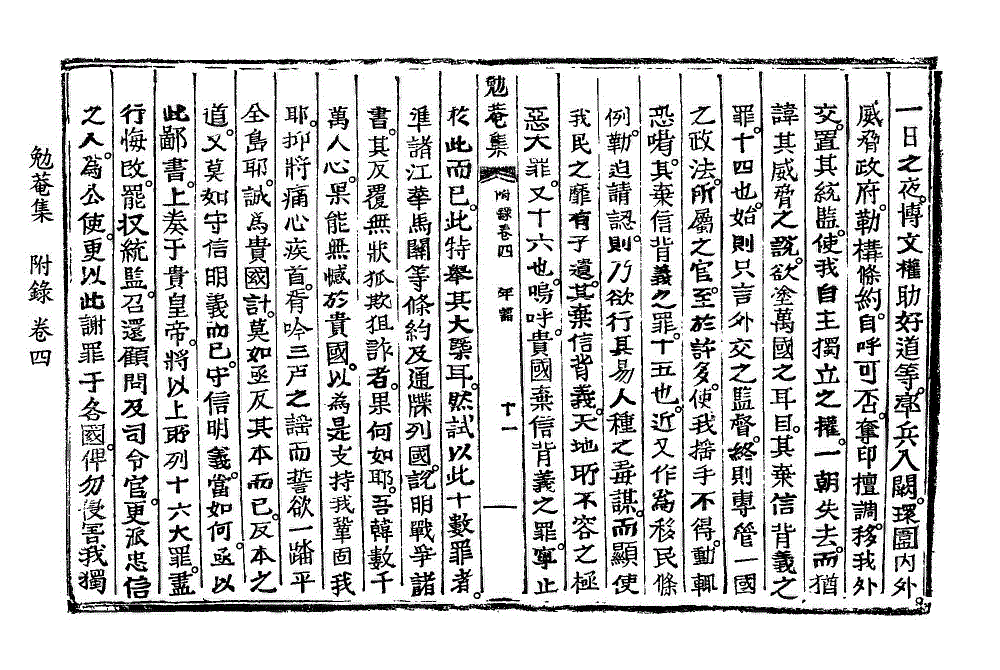 一日之夜。博文权助好道等。率兵入阙。环围内外。威胁政府。勒构条约。自呼可否。夺印擅调。移我外交。置其统监。使我自主独立之权。一朝失去。而犹讳其威胁之说。欲涂万国之耳目。其弃信背义之罪。十四也。始则只言外交之监督。终则专管一国之政法。所属之官。至于许多。使我摇手不得。动辄恐喝。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五也。近又作为移民条例。勒迫请认。则乃欲行其易人种之毒谋。而显使我民之靡有子遗。其弃信背义。天地所不容之极恶大罪。又十六也。呜呼。贵国弃信背义之罪。宁止于此而已。此特举其大槩耳。然试以此十数罪者。准诸江华马关等条约及通牒列国。说明战争诸书。其反覆无状狐欺狙诈者。果何如耶。吾韩数千万人心。果能无憾于贵国。以为是支持我巩固我耶。抑将痛心疾首。胥吟三户之谣而誓欲一踏平全岛耶。诚为贵国计。莫如亟反其本而已。反本之道。又莫如守信明义而已。守信明义。当如何。亟以此鄙书。上奏于贵皇帝。将以上所列十六大罪。尽行悔改。罢收统监。召还顾问及司令官。更派忠信之人。为公使。更以此谢罪于各国。俾勿侵害我独
一日之夜。博文权助好道等。率兵入阙。环围内外。威胁政府。勒构条约。自呼可否。夺印擅调。移我外交。置其统监。使我自主独立之权。一朝失去。而犹讳其威胁之说。欲涂万国之耳目。其弃信背义之罪。十四也。始则只言外交之监督。终则专管一国之政法。所属之官。至于许多。使我摇手不得。动辄恐喝。其弃信背义之罪。十五也。近又作为移民条例。勒迫请认。则乃欲行其易人种之毒谋。而显使我民之靡有子遗。其弃信背义。天地所不容之极恶大罪。又十六也。呜呼。贵国弃信背义之罪。宁止于此而已。此特举其大槩耳。然试以此十数罪者。准诸江华马关等条约及通牒列国。说明战争诸书。其反覆无状狐欺狙诈者。果何如耶。吾韩数千万人心。果能无憾于贵国。以为是支持我巩固我耶。抑将痛心疾首。胥吟三户之谣而誓欲一踏平全岛耶。诚为贵国计。莫如亟反其本而已。反本之道。又莫如守信明义而已。守信明义。当如何。亟以此鄙书。上奏于贵皇帝。将以上所列十六大罪。尽行悔改。罢收统监。召还顾问及司令官。更派忠信之人。为公使。更以此谢罪于各国。俾勿侵害我独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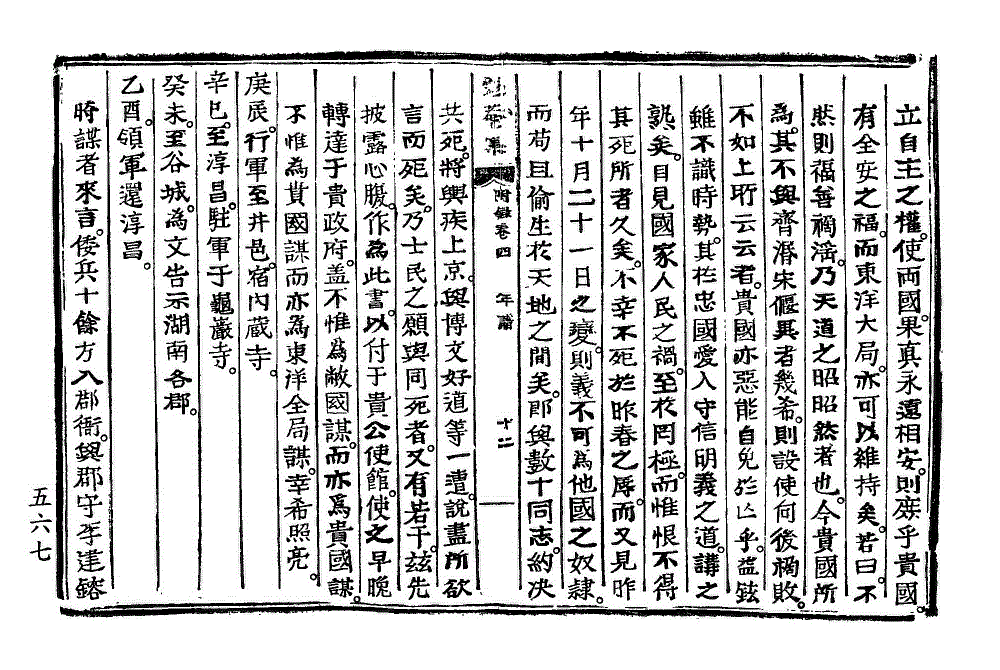 立自主之权。使两国。果真永远相安。则庶乎贵国。有全安之福。而东洋大局。亦可以维持矣。若曰。不然则福善𥚁淫。乃天道之昭昭然者也。今贵国所为。其不与齐湣宋偃异者几希。则设使向后𥚁败。不如上所云云者。贵国亦恶能自免于亡乎。益铉虽不识时势。其于忠国爱人守信明义之道。讲之熟矣。目见国家人民之祸。至于罔极。而惟恨不得其死所者久矣。不幸不死于昨春之辱。而又见昨年十月二十一日之变。则义不可为他国之奴隶。而苟且偷生于天地之间矣。即与数十同志。约决共死。将舆疾上京。与博文好道等一遭。说尽所欲言而死矣。乃士民之愿与同死者。又有若干。玆先披露心腹。作为此书。以付于贵公使馆。使之早晚转达于贵政府。盖不惟为敝国谋。而亦为贵国谋。不惟为贵国谋而亦为东洋全局谋。幸希照亮。
立自主之权。使两国。果真永远相安。则庶乎贵国。有全安之福。而东洋大局。亦可以维持矣。若曰。不然则福善𥚁淫。乃天道之昭昭然者也。今贵国所为。其不与齐湣宋偃异者几希。则设使向后𥚁败。不如上所云云者。贵国亦恶能自免于亡乎。益铉虽不识时势。其于忠国爱人守信明义之道。讲之熟矣。目见国家人民之祸。至于罔极。而惟恨不得其死所者久矣。不幸不死于昨春之辱。而又见昨年十月二十一日之变。则义不可为他国之奴隶。而苟且偷生于天地之间矣。即与数十同志。约决共死。将舆疾上京。与博文好道等一遭。说尽所欲言而死矣。乃士民之愿与同死者。又有若干。玆先披露心腹。作为此书。以付于贵公使馆。使之早晚转达于贵政府。盖不惟为敝国谋。而亦为贵国谋。不惟为贵国谋而亦为东洋全局谋。幸希照亮。庚辰。行军至井邑。宿内藏寺。
辛巳。至淳昌。驻军于龟岩寺。
癸未。至谷城。为文告示湖南各郡。
乙酉。领军还淳昌。
时谍者来言。倭兵十馀方入郡衙。与郡守李建镕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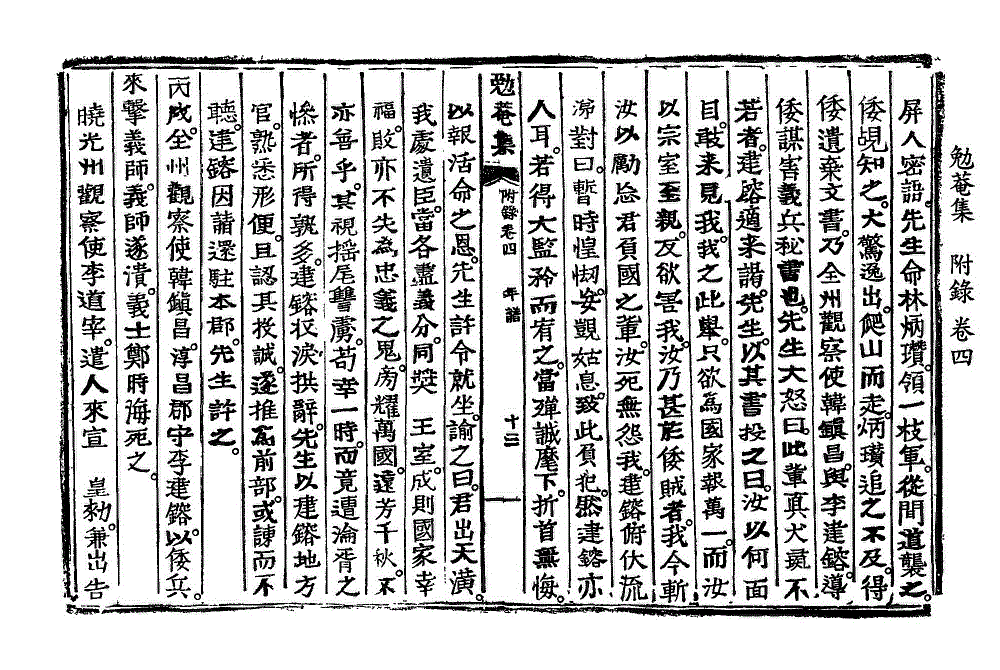 屏人密语。先生命林炳瓒。领一枝军。从间道袭之。倭觇知之。大惊逸出。爬山而走。炳瓒追之不及。得倭遗弃文书。乃全州观察使韩镇昌。与李建镕。导倭谋害义兵秘书也。先生大怒曰。此辈真犬彘不若者。建镕适来谒。先生。以其书投之曰。汝以何面目。敢来见我。我之此举。只欲为国家报万一。而汝以宗室至亲。反欲害我。汝乃甚于倭贼者。我今斩汝以励忘君负国之辈。汝死无怨我。建镕俯伏流涕对曰。暂时惶㥘。妄觊姑息。致此负犯。然建镕亦人耳。若得大监矜而宥之。当殚诚麾下。折首无悔。以报活命之恩。先生许令就坐。谕之曰。君出天潢。我处遗臣。当各尽义分。同奖 王室。成则国家幸福。败亦不失为忠义之鬼。旁耀万国。远芳千秋。不亦善乎。其视摇尾雠虏。苟幸一时。而竟遭沦胥之惨者。所得孰多。建镕收泪拱辞。先生以建镕地方官。熟悉形便。且认其投诚。遂推为前部。或谏而不听。建镕因请还驻本郡。先生许之。
屏人密语。先生命林炳瓒。领一枝军。从间道袭之。倭觇知之。大惊逸出。爬山而走。炳瓒追之不及。得倭遗弃文书。乃全州观察使韩镇昌。与李建镕。导倭谋害义兵秘书也。先生大怒曰。此辈真犬彘不若者。建镕适来谒。先生。以其书投之曰。汝以何面目。敢来见我。我之此举。只欲为国家报万一。而汝以宗室至亲。反欲害我。汝乃甚于倭贼者。我今斩汝以励忘君负国之辈。汝死无怨我。建镕俯伏流涕对曰。暂时惶㥘。妄觊姑息。致此负犯。然建镕亦人耳。若得大监矜而宥之。当殚诚麾下。折首无悔。以报活命之恩。先生许令就坐。谕之曰。君出天潢。我处遗臣。当各尽义分。同奖 王室。成则国家幸福。败亦不失为忠义之鬼。旁耀万国。远芳千秋。不亦善乎。其视摇尾雠虏。苟幸一时。而竟遭沦胥之惨者。所得孰多。建镕收泪拱辞。先生以建镕地方官。熟悉形便。且认其投诚。遂推为前部。或谏而不听。建镕因请还驻本郡。先生许之。丙戌。全州观察使韩镇昌。淳昌郡守李建镕。以倭兵。来击义师。义师遂溃。义士郑时海死之。
晓光州观察使李道宰。遣人来宣 皇敕。兼出告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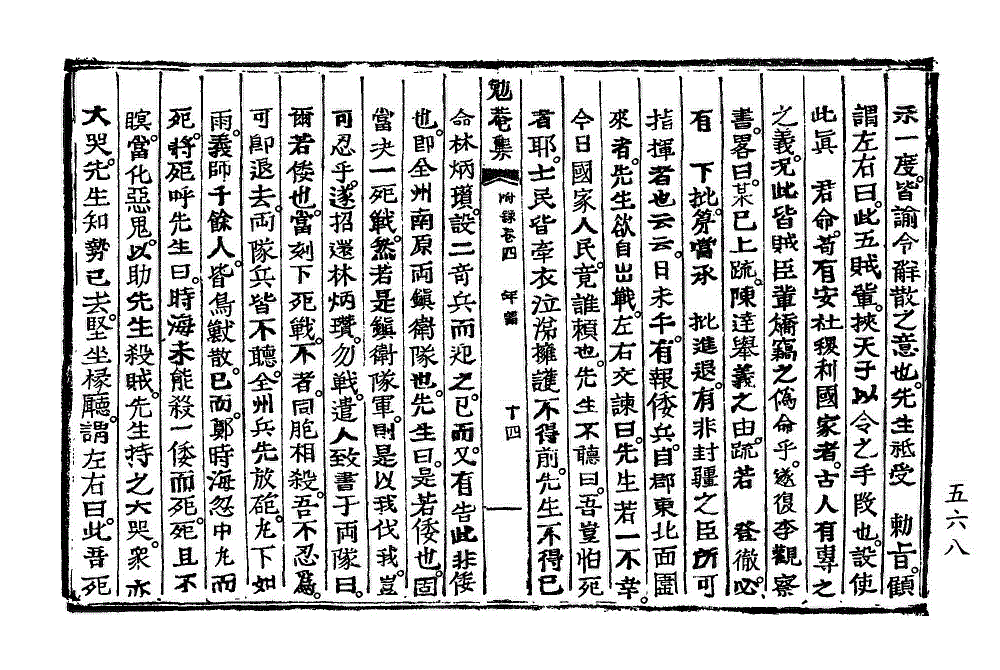 示一度。皆谕令解散之意也。先生祗受 敕旨。顾谓左右曰。此五贼辈。挟天子以令之手段也。设使此真 君命。苟有安社稷利国家者。古人有专之之义。况此皆贼臣辈矫窃之伪命乎。遂复李观察书。略曰。某已上疏。陈达举义之由。疏若 登彻。必有 下批。第当承 批进退。有非封疆之臣所可指挥者也云云。日未午。有报倭兵。自郡东北面围来者。先生欲自出战。左右交谏曰。先生若一不幸。今日国家人民。竟谁赖也。先生不听曰。吾岂怕死者耶。士民皆牵衣泣涕拥护不得前。先生不得已命林炳瓒。设二奇兵而迎之。已而。又有告此非倭也。即全州南原两镇卫队也。先生曰。是若倭也。固当决一死战。然若是镇卫队军。则是以我伐我。岂可忍乎。遂招还林炳瓒。勿战。遣人致书于两队曰。尔若倭也。当刻下死战。不者。同胞相杀。吾不忍为。可即退去。两队兵皆不听。全州兵先放炮。丸下如雨。义师千馀人。皆鸟兽散。已而。郑时海忽中丸而死。将死呼先生曰。时海未能杀一倭而死。死且不瞑。当化恶鬼。以助先生杀贼。先生持之大哭。众亦大哭。先生知势已去。坚坐椽厅。谓左右曰。此吾死
示一度。皆谕令解散之意也。先生祗受 敕旨。顾谓左右曰。此五贼辈。挟天子以令之手段也。设使此真 君命。苟有安社稷利国家者。古人有专之之义。况此皆贼臣辈矫窃之伪命乎。遂复李观察书。略曰。某已上疏。陈达举义之由。疏若 登彻。必有 下批。第当承 批进退。有非封疆之臣所可指挥者也云云。日未午。有报倭兵。自郡东北面围来者。先生欲自出战。左右交谏曰。先生若一不幸。今日国家人民。竟谁赖也。先生不听曰。吾岂怕死者耶。士民皆牵衣泣涕拥护不得前。先生不得已命林炳瓒。设二奇兵而迎之。已而。又有告此非倭也。即全州南原两镇卫队也。先生曰。是若倭也。固当决一死战。然若是镇卫队军。则是以我伐我。岂可忍乎。遂招还林炳瓒。勿战。遣人致书于两队曰。尔若倭也。当刻下死战。不者。同胞相杀。吾不忍为。可即退去。两队兵皆不听。全州兵先放炮。丸下如雨。义师千馀人。皆鸟兽散。已而。郑时海忽中丸而死。将死呼先生曰。时海未能杀一倭而死。死且不瞑。当化恶鬼。以助先生杀贼。先生持之大哭。众亦大哭。先生知势已去。坚坐椽厅。谓左右曰。此吾死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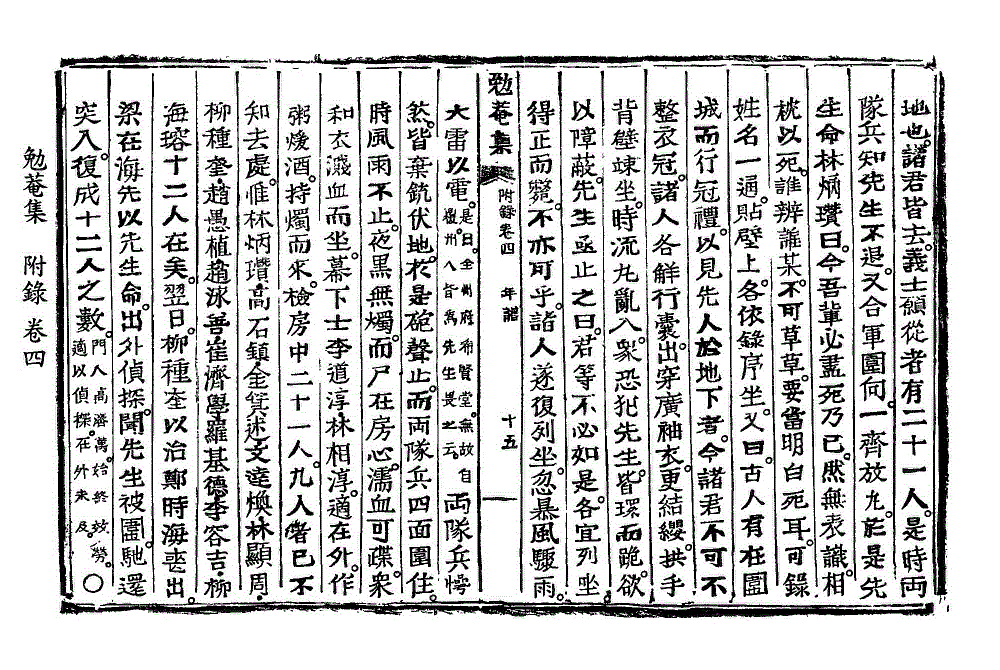 地也。诸君皆去。义士愿从者有二十一人。是时两队兵知先生不退。又合军围向。一齐放丸。于是先生命林炳瓒曰。今吾辈必尽死乃已。然无表识。相枕以死。谁辨谁某。不可草草。要当明白死耳。可录姓名一通。贴壁上。各依录序坐。又曰。古人有在围城而行冠礼。以见先人于地下者。今诸君不可不整衣冠。诸人各解行囊。出穿广袖衣。更结缨。拱手背壁竦坐。时流丸乱入。众恐犯先生。皆环而跪。欲以障蔽。先生亟止之曰。君等不必如是。各宜列坐。得正而毙。不亦可乎。诸人遂复列坐。忽暴风骤雨。大雷以电。(是日。全州府希贤堂。无故自覆。州人皆为先生畏之云。)两队兵愕然。皆弃铳伏地。于是炮声止。而两队兵四面围住。时风雨不止。夜黑无烛。而尸在房心。濡血可蹀。众和衣溅血而坐。幕下士李道淳,林相淳。适在外。作粥煖酒。持烛而来。检房中二十一人。九人者已不知去处。惟林炳瓒,高石镇,金箕述,文达焕,林显周,柳种奎,赵愚植,赵泳善,崔济学,罗基德,李容吉,柳海瑢十二人在矣。翌日。柳种奎以治郑时海丧出。梁在海先以先生命。出外侦探。闻先生被围。驰还突入。复成十二人之数。(门人高济万。始终效劳。适以侦探。在外未及。)○
地也。诸君皆去。义士愿从者有二十一人。是时两队兵知先生不退。又合军围向。一齐放丸。于是先生命林炳瓒曰。今吾辈必尽死乃已。然无表识。相枕以死。谁辨谁某。不可草草。要当明白死耳。可录姓名一通。贴壁上。各依录序坐。又曰。古人有在围城而行冠礼。以见先人于地下者。今诸君不可不整衣冠。诸人各解行囊。出穿广袖衣。更结缨。拱手背壁竦坐。时流丸乱入。众恐犯先生。皆环而跪。欲以障蔽。先生亟止之曰。君等不必如是。各宜列坐。得正而毙。不亦可乎。诸人遂复列坐。忽暴风骤雨。大雷以电。(是日。全州府希贤堂。无故自覆。州人皆为先生畏之云。)两队兵愕然。皆弃铳伏地。于是炮声止。而两队兵四面围住。时风雨不止。夜黑无烛。而尸在房心。濡血可蹀。众和衣溅血而坐。幕下士李道淳,林相淳。适在外。作粥煖酒。持烛而来。检房中二十一人。九人者已不知去处。惟林炳瓒,高石镇,金箕述,文达焕,林显周,柳种奎,赵愚植,赵泳善,崔济学,罗基德,李容吉,柳海瑢十二人在矣。翌日。柳种奎以治郑时海丧出。梁在海先以先生命。出外侦探。闻先生被围。驰还突入。复成十二人之数。(门人高济万。始终效劳。适以侦探。在外未及。)○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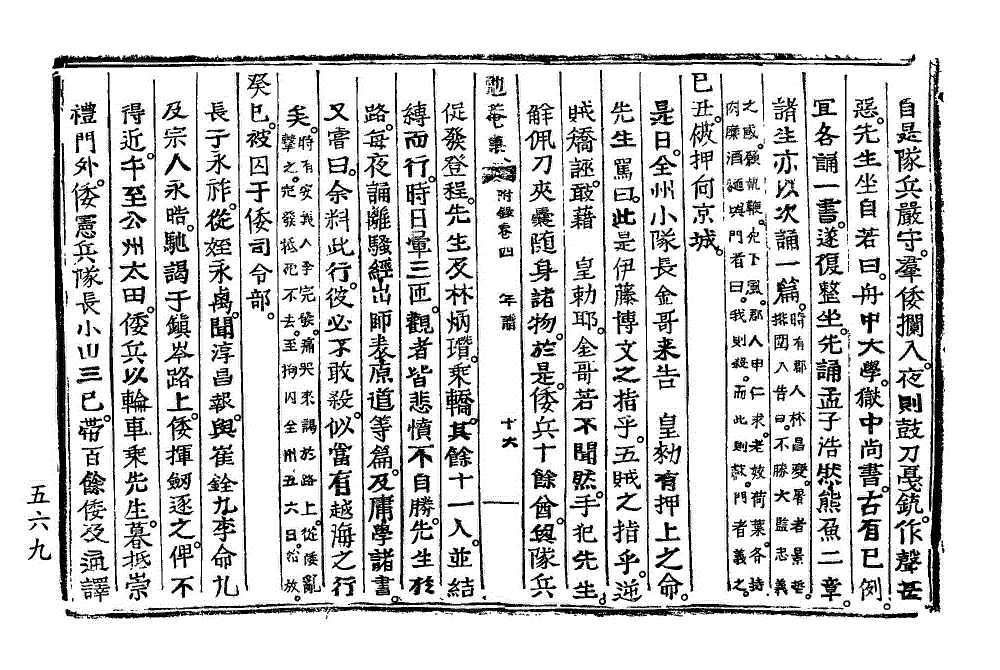 自是队兵严守。群倭拦入。夜则鼓刀戛铳。作声甚恶。先生坐自若曰。舟中大学。狱中尚书。古有已例。宜各诵一书。遂复整坐。先诵孟子浩然,熊鱼二章。诸生亦以次诵一篇。(时有郡人林昌燮。屠者景哲。排围入告曰。不胜大监忠义之感。愿执鞭。死下风。郡人申仁求。老姣荷叶。各持肉糜酒面与门者曰。我则杀。而此则献。门者义之。)
自是队兵严守。群倭拦入。夜则鼓刀戛铳。作声甚恶。先生坐自若曰。舟中大学。狱中尚书。古有已例。宜各诵一书。遂复整坐。先诵孟子浩然,熊鱼二章。诸生亦以次诵一篇。(时有郡人林昌燮。屠者景哲。排围入告曰。不胜大监忠义之感。愿执鞭。死下风。郡人申仁求。老姣荷叶。各持肉糜酒面与门者曰。我则杀。而此则献。门者义之。)己丑。被押向京城。
是日。全州小队长金哥来告 皇敕有押上之命。先生骂曰。此是伊藤博文之指乎。五贼之指乎。逆贼矫诬。敢藉 皇敕耶。金哥若不闻然。手犯先生。解佩刀夹囊随身诸物。于是。倭兵十馀酋。与队兵促发登程。先生及林炳瓒。乘轿。其馀十一人。并结缚而行。时日晕三匝。观者皆悲愤不自胜。先生于路。每夜诵离骚经,出师表,原道等篇。及庸,学诸书。又尝曰。余料此行。彼必不敢杀。似当有越海之行矣。(时有安义人李完发。痛哭来谒于路上。从倭乱击之。完发牴死不去。至拘囚全州五六日。始放。)
癸巳。被囚于倭司令部。
长子永祚。从侄永卨。闻淳昌报。与崔铨九,李命九及宗人永皓。驰谒于镇岑路上。倭挥剑逐之。俾不得近。午至公州太田。倭兵以轮车乘先生。暮抵崇礼门外。倭宪兵队长小山三巳。带百馀倭及通译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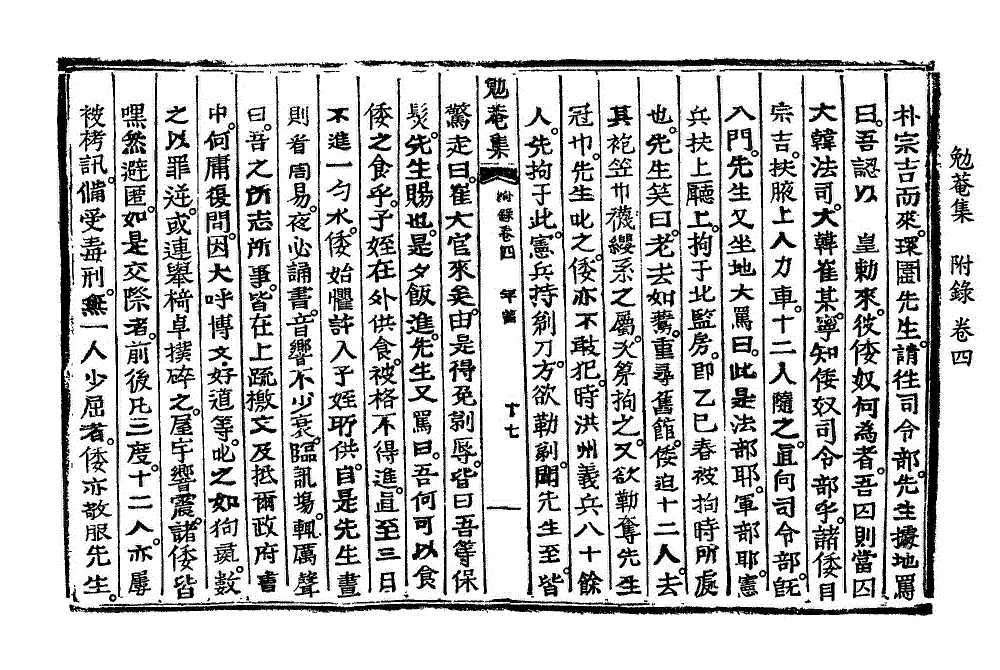 朴宗吉而来。环围先生。请往司令部。先生据地骂曰。吾认以 皇敕来。彼倭奴何为者。吾囚则当囚大韩法司。大韩崔某。宁知倭奴司令部乎。诸倭目宗吉。扶腋上人力车。十二人随之。直向司令部。既入门。先生又坐地大骂曰。此是法部耶。军部耶。宪兵扶上厅上。拘于北监房。即乙巳春被拘时所处也。先生笑曰。老去如燕。重寻旧馆。倭迫十二人。去其袍笠巾袜缨系之属。次第拘之。又欲勒夺先生冠巾。先生叱之。倭亦不敢犯。时洪州义兵八十馀人。先拘于此。宪兵持剃刀。方欲勒剃。闻先生至。皆惊走曰。崔大官来矣。由是得免剃辱。皆曰吾等保发。先生赐也。是夕饭进。先生又骂曰。吾何可以食倭之食乎。子侄在外供食。被格不得进。直至三日不进一勺水。倭始惧许入子侄所供。自是先生昼则看周易。夜必诵书。音响不少衰。临讯场。辄厉声曰。吾之所志所事。皆在上疏檄文及抵尔政府书中。何庸复问。因大呼博文,好道等。叱之如狗彘。数之以罪逆。或连举椅卓扑碎之。屋宇响震。诸倭皆嘿然避匿。如是交际者。前后凡三度。十二人。亦屡被栲讯。备受毒刑。无一人少屈者。倭亦敬服先生。
朴宗吉而来。环围先生。请往司令部。先生据地骂曰。吾认以 皇敕来。彼倭奴何为者。吾囚则当囚大韩法司。大韩崔某。宁知倭奴司令部乎。诸倭目宗吉。扶腋上人力车。十二人随之。直向司令部。既入门。先生又坐地大骂曰。此是法部耶。军部耶。宪兵扶上厅上。拘于北监房。即乙巳春被拘时所处也。先生笑曰。老去如燕。重寻旧馆。倭迫十二人。去其袍笠巾袜缨系之属。次第拘之。又欲勒夺先生冠巾。先生叱之。倭亦不敢犯。时洪州义兵八十馀人。先拘于此。宪兵持剃刀。方欲勒剃。闻先生至。皆惊走曰。崔大官来矣。由是得免剃辱。皆曰吾等保发。先生赐也。是夕饭进。先生又骂曰。吾何可以食倭之食乎。子侄在外供食。被格不得进。直至三日不进一勺水。倭始惧许入子侄所供。自是先生昼则看周易。夜必诵书。音响不少衰。临讯场。辄厉声曰。吾之所志所事。皆在上疏檄文及抵尔政府书中。何庸复问。因大呼博文,好道等。叱之如狗彘。数之以罪逆。或连举椅卓扑碎之。屋宇响震。诸倭皆嘿然避匿。如是交际者。前后凡三度。十二人。亦屡被栲讯。备受毒刑。无一人少屈者。倭亦敬服先生。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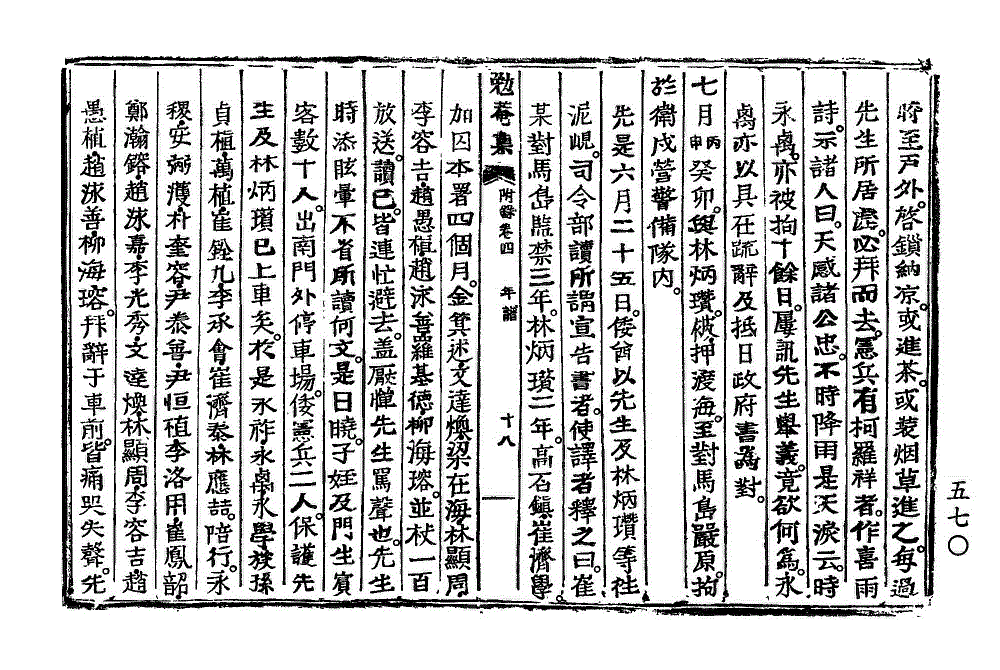 时至户外。启锁纳凉。或进茶。或装烟草进之。每过先生所居处。必拜而去。宪兵有柯罗祥者。作喜雨诗。示诸人曰。天感诸公忠。不时降雨是天泪云。时永卨。亦被拘十馀日。屡讯先生举义。竟欲何为。永卨亦以具在疏辞及抵日政府书为对。
时至户外。启锁纳凉。或进茶。或装烟草进之。每过先生所居处。必拜而去。宪兵有柯罗祥者。作喜雨诗。示诸人曰。天感诸公忠。不时降雨是天泪云。时永卨。亦被拘十馀日。屡讯先生举义。竟欲何为。永卨亦以具在疏辞及抵日政府书为对。七月(丙申)癸卯。与林炳瓒。被押渡海。至对马岛严原。拘于卫戍营警备队内。
先是六月二十五日。倭酋以先生及林炳瓒等往泥岘。司令部读所谓宣告书者。使译者释之曰。崔某对马岛监禁三年。林炳瓒二年。高石镇,崔济学。加囚本署四个月。金箕述,文达焕,梁在海,林显周,李容吉,赵愚植,赵泳善,罗基德,柳海瑢。并杖一百放送。读已。皆连忙避去。盖厌惮先生骂声也。先生时添眩晕不省所读何文。是日晓。子侄及门生宾客数十人。出南门外停车场。倭宪兵二人。保护先生及林炳瓒已上车矣。于是永祚,永卨,永学,族孙贞植,万植,崔铨九,李承会,崔济泰,林应哲。陪行。永稷,安弼濩,朴奎容,尹泰善,尹恒植,李洛用,崔凤韶,郑瀚镕,赵泳嘉,李光秀,文达焕,林显周,李容吉,赵愚植,赵泳善,柳海瑢。拜辞于车前。皆痛哭失声。先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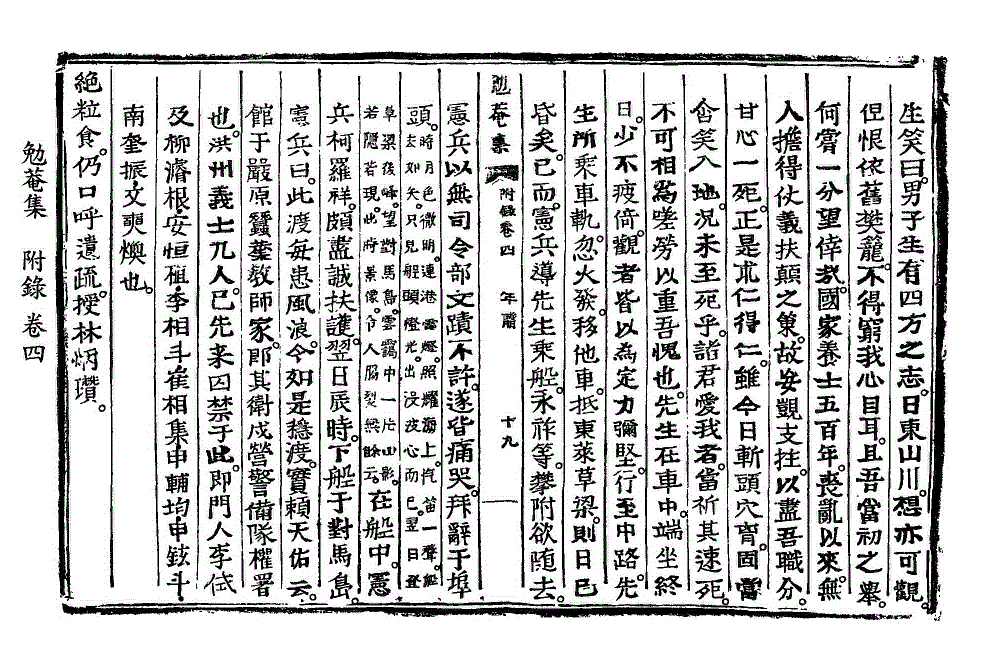 生笑曰。男子生有四方之志。日东山川。想亦可观。但恨依旧樊笼。不得穷我心目耳。且吾当初之举。何尝一分望倖哉。国家养士五百年。丧乱以来。无人担得仗义扶颠之策。故妄觊支拄。以尽吾职分。甘心一死。正是求仁得仁。虽今日斩头穴胸。固当含笑入地。况未至死乎。诸君爱我者。当祈其速死。不可相为嗟劳以重吾愧也。先生在车中。端坐终日。少不疲倚。观者皆以为定力弥坚。行至中路。先生所乘车轨。忽火发。移他车。抵东莱草梁。则日已昏矣。已而。宪兵导先生乘船。永祚等。攀附欲随去。宪兵以无司令部文迹不许。遂皆痛哭。拜辞于埠头。(时月色微明。连港电灯。照耀海上。汽笛一声。船去如矢。只见船头灯光。出没波心而已。翌日登草梁后峰。望对马岛。云霭中一片山影。若隐若现。此时景像。令人肠裂无馀云。)在船中。宪兵柯罗祥。颇尽诚扶护。翌日辰时。下船于对马岛。宪兵曰。此渡每患风浪。今如是稳渡。实赖天佑云。馆于严原蚕业教师家。即其卫戍营警备队权署也。洪州义士九人。已先来囚禁于此。即门人李侙及柳浚根,安恒植,李相斗,崔相集,申辅均,申铉斗,南奎振,文奭焕也。
生笑曰。男子生有四方之志。日东山川。想亦可观。但恨依旧樊笼。不得穷我心目耳。且吾当初之举。何尝一分望倖哉。国家养士五百年。丧乱以来。无人担得仗义扶颠之策。故妄觊支拄。以尽吾职分。甘心一死。正是求仁得仁。虽今日斩头穴胸。固当含笑入地。况未至死乎。诸君爱我者。当祈其速死。不可相为嗟劳以重吾愧也。先生在车中。端坐终日。少不疲倚。观者皆以为定力弥坚。行至中路。先生所乘车轨。忽火发。移他车。抵东莱草梁。则日已昏矣。已而。宪兵导先生乘船。永祚等。攀附欲随去。宪兵以无司令部文迹不许。遂皆痛哭。拜辞于埠头。(时月色微明。连港电灯。照耀海上。汽笛一声。船去如矢。只见船头灯光。出没波心而已。翌日登草梁后峰。望对马岛。云霭中一片山影。若隐若现。此时景像。令人肠裂无馀云。)在船中。宪兵柯罗祥。颇尽诚扶护。翌日辰时。下船于对马岛。宪兵曰。此渡每患风浪。今如是稳渡。实赖天佑云。馆于严原蚕业教师家。即其卫戍营警备队权署也。洪州义士九人。已先来囚禁于此。即门人李侙及柳浚根,安恒植,李相斗,崔相集,申辅均,申铉斗,南奎振,文奭焕也。绝粒食。仍口呼遗疏。授林炳瓒。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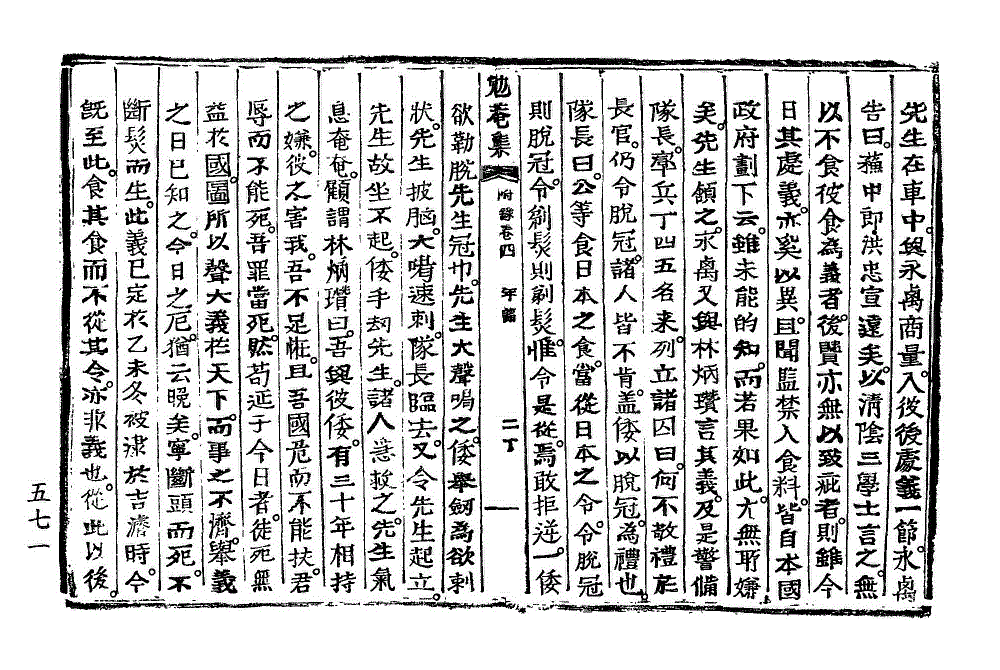 先生在车中。与永卨商量。入彼后处义一节。永卨告曰。苏中郎,洪忠宣远矣。以清阴三学士言之。无以不食彼食为义者。后贤亦无以致疵者。则虽今日其处义。亦奚以异。且闻监禁人食料。皆自本国政府划下云。虽未能的知。而若果如此。尤无所嫌矣。先生颔之。永卨又与林炳瓒言其义。及是警备队长。率兵丁四五名来。列立诸囚曰。何不敬礼于长官。仍令脱冠。诸人皆不肯。盖倭以脱冠。为礼也。队长曰。公等食日本之食。当从日本之令。令脱冠则脱冠。令剃发则剃发。惟令是从。焉敢拒逆。一倭欲勒脱先生冠巾。先生大声喝之。倭举剑为欲刺状。先生披胸。大喝速刺。队长临去。又令先生起立。先生故坐不起。倭手劫先生。诸人急救之。先生气息奄奄。顾谓林炳瓒曰。吾与彼倭。有三十年相持之嫌。彼之害我。吾不足怪。且吾国危而不能扶。君辱而不能死。吾罪当死。然苟延于今日者。徒死无益于国。图所以声大义于天下。而事之不济。举义之日已知之。今日之厄。犹云晚矣。宁断头而死。不断发而生。此义已定于乙未冬被逮于吉浚时。今既至此。食其食而不从其令。亦非义也。从此以后。
先生在车中。与永卨商量。入彼后处义一节。永卨告曰。苏中郎,洪忠宣远矣。以清阴三学士言之。无以不食彼食为义者。后贤亦无以致疵者。则虽今日其处义。亦奚以异。且闻监禁人食料。皆自本国政府划下云。虽未能的知。而若果如此。尤无所嫌矣。先生颔之。永卨又与林炳瓒言其义。及是警备队长。率兵丁四五名来。列立诸囚曰。何不敬礼于长官。仍令脱冠。诸人皆不肯。盖倭以脱冠。为礼也。队长曰。公等食日本之食。当从日本之令。令脱冠则脱冠。令剃发则剃发。惟令是从。焉敢拒逆。一倭欲勒脱先生冠巾。先生大声喝之。倭举剑为欲刺状。先生披胸。大喝速刺。队长临去。又令先生起立。先生故坐不起。倭手劫先生。诸人急救之。先生气息奄奄。顾谓林炳瓒曰。吾与彼倭。有三十年相持之嫌。彼之害我。吾不足怪。且吾国危而不能扶。君辱而不能死。吾罪当死。然苟延于今日者。徒死无益于国。图所以声大义于天下。而事之不济。举义之日已知之。今日之厄。犹云晚矣。宁断头而死。不断发而生。此义已定于乙未冬被逮于吉浚时。今既至此。食其食而不从其令。亦非义也。从此以后。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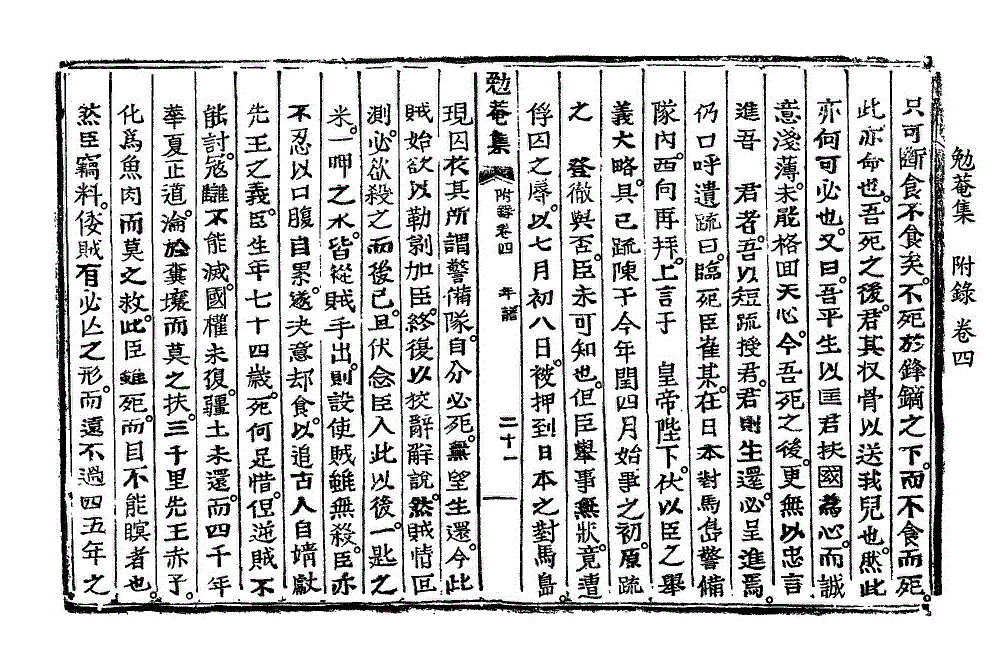 只可断食不食矣。不死于锋镝之下。而不食而死。此亦命也。吾死之后。君其收骨以送我儿也。然此亦何可必也。又曰。吾平生以匡君扶国为心。而诚意浅薄。未能格回天心。今吾死之后。更无以忠言进吾 君者。吾以短疏授君。君则生还。必呈进焉。仍口呼遗疏曰。临死臣崔某。在日本对马岛警备队内。西向再拜。上言于 皇帝陛下。伏以臣之举义大略。具已疏陈于今年闰四月始事之初。原疏之 登彻与否。臣未可知也。但臣举事无状。竟遭俘囚之辱。以七月初八日。被押到日本之对马岛。现囚于其所谓警备队。自分必死。无望生还。今此贼始欲以勒剃加臣。终复以狡辞解说。然贼情叵测。必欲杀之而后已。且伏念臣入此以后。一匙之米。一呷之水。皆从贼手出。则设使贼虽无杀。臣亦不忍以口腹自累。遂决意却食。以追古人自靖献先王之义。臣生年七十四岁。死何足惜。但逆贼不能讨。寇雠不能灭。国权未复。疆土未还。而四千年华夏正道。沦于粪壤而莫之扶。三千里先王赤子。化为鱼肉而莫之救。此臣虽死。而目不能瞑者也。然臣窃料。倭贼有必亡之形。而远不过四五年之
只可断食不食矣。不死于锋镝之下。而不食而死。此亦命也。吾死之后。君其收骨以送我儿也。然此亦何可必也。又曰。吾平生以匡君扶国为心。而诚意浅薄。未能格回天心。今吾死之后。更无以忠言进吾 君者。吾以短疏授君。君则生还。必呈进焉。仍口呼遗疏曰。临死臣崔某。在日本对马岛警备队内。西向再拜。上言于 皇帝陛下。伏以臣之举义大略。具已疏陈于今年闰四月始事之初。原疏之 登彻与否。臣未可知也。但臣举事无状。竟遭俘囚之辱。以七月初八日。被押到日本之对马岛。现囚于其所谓警备队。自分必死。无望生还。今此贼始欲以勒剃加臣。终复以狡辞解说。然贼情叵测。必欲杀之而后已。且伏念臣入此以后。一匙之米。一呷之水。皆从贼手出。则设使贼虽无杀。臣亦不忍以口腹自累。遂决意却食。以追古人自靖献先王之义。臣生年七十四岁。死何足惜。但逆贼不能讨。寇雠不能灭。国权未复。疆土未还。而四千年华夏正道。沦于粪壤而莫之扶。三千里先王赤子。化为鱼肉而莫之救。此臣虽死。而目不能瞑者也。然臣窃料。倭贼有必亡之形。而远不过四五年之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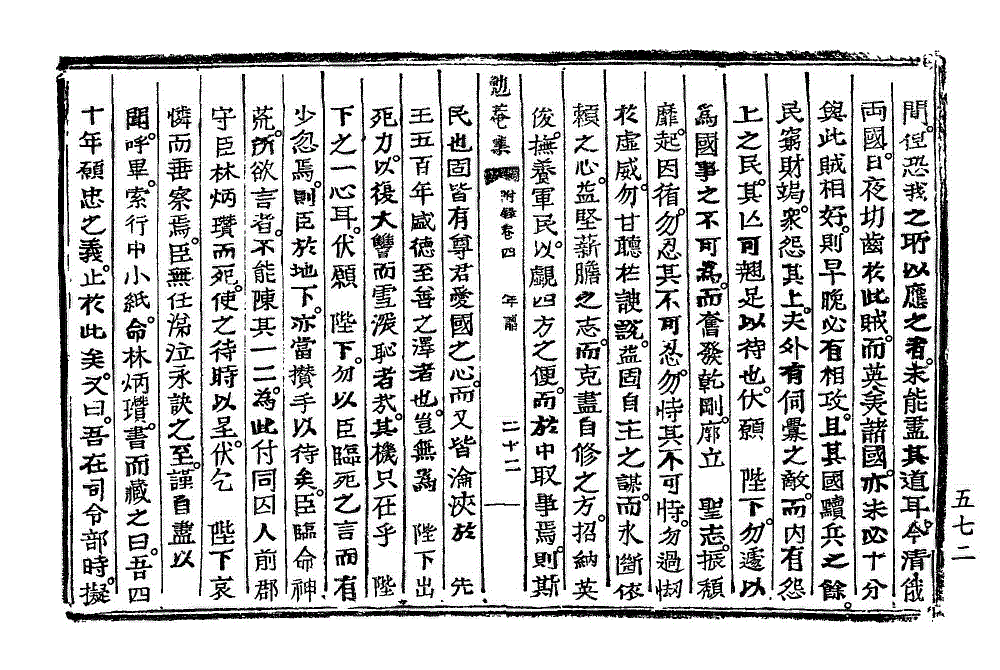 间。但恐我之所以应之者。未能尽其道耳。今清,俄两国。日夜切齿于此贼。而英,美诸国。亦未必十分与此贼相好。则早晚必有相攻。且其国黩兵之馀。民穷财竭。众怨其上。夫外有伺衅之敌。而内有怨上之民。其亡可翘足以待也。伏愿 陛下。勿遽以为国事之不可为。而奋发乾刚。廓立 圣志。振颓靡。起因循。勿忍其不可忍。勿恃其不可恃。勿过㥘于虚威。勿甘听于谀说。益固自主之谋。而永断依赖之心。益坚薪胆之志。而克尽自修之方。招纳英俊。抚养军民。以觑四方之便。而于中取事焉。则斯民也固皆有尊君爱国之心。而又皆沦浃于 先王五百年盛德至善之泽者也。岂无为 陛下出死力。以复大雠而雪深耻者哉。其机只在乎 陛下之一心耳。伏愿 陛下。勿以臣临死之言而有少忽焉。则臣于地下。亦当攒手以待矣。臣临命神荒。所欲言者。不能陈其一二。为此付同囚人前郡守臣林炳瓒而死。使之待时以呈。伏乞 陛下哀怜而垂察焉。臣无任涕泣永诀之至。谨自尽以 闻。呼毕。索行中小纸。命林炳瓒。书而藏之曰。吾四十年愿忠之义。止于此矣。又曰。吾在司令部时。拟
间。但恐我之所以应之者。未能尽其道耳。今清,俄两国。日夜切齿于此贼。而英,美诸国。亦未必十分与此贼相好。则早晚必有相攻。且其国黩兵之馀。民穷财竭。众怨其上。夫外有伺衅之敌。而内有怨上之民。其亡可翘足以待也。伏愿 陛下。勿遽以为国事之不可为。而奋发乾刚。廓立 圣志。振颓靡。起因循。勿忍其不可忍。勿恃其不可恃。勿过㥘于虚威。勿甘听于谀说。益固自主之谋。而永断依赖之心。益坚薪胆之志。而克尽自修之方。招纳英俊。抚养军民。以觑四方之便。而于中取事焉。则斯民也固皆有尊君爱国之心。而又皆沦浃于 先王五百年盛德至善之泽者也。岂无为 陛下出死力。以复大雠而雪深耻者哉。其机只在乎 陛下之一心耳。伏愿 陛下。勿以臣临死之言而有少忽焉。则臣于地下。亦当攒手以待矣。臣临命神荒。所欲言者。不能陈其一二。为此付同囚人前郡守臣林炳瓒而死。使之待时以呈。伏乞 陛下哀怜而垂察焉。臣无任涕泣永诀之至。谨自尽以 闻。呼毕。索行中小纸。命林炳瓒。书而藏之曰。吾四十年愿忠之义。止于此矣。又曰。吾在司令部时。拟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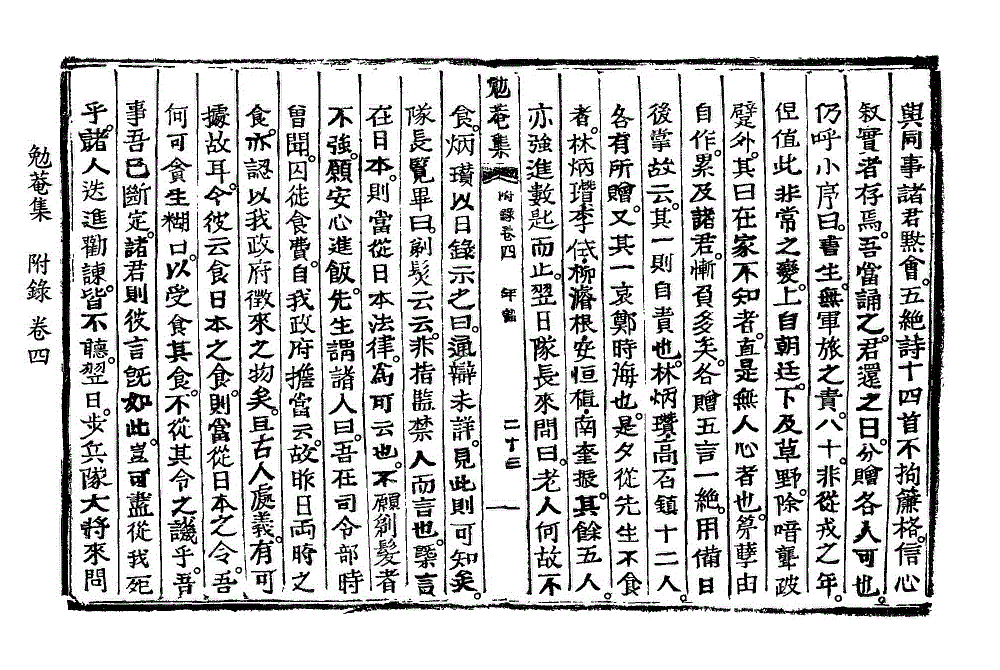 与同事诸君默会。五绝诗十四首不拘帘格。信心叙实者存焉。吾当诵之。君还之日。分赠各人可也。仍呼小序曰。书生。无军旅之责。八十。非从戎之年。但值此非常之变。上自朝廷。下及草野。除喑聋跛躄外。其曰在家不知者。直是无人心者也。第孽由自作。累及诸君。惭负多矣。各赠五言一绝。用备日后掌故云。其一则自责也。林炳瓒,高石镇十二人。各有所赠。又其一哀郑时海也。是夕从先生不食者。林炳瓒,李侙,柳浚根,安恒植,南奎振。其馀五人。亦强进数匙而止。翌日队长来问曰。老人何故不食。炳瓒以日录示之曰。通辩未详。见此则可知矣。队长览毕曰。剃发云云。非指监禁人而言也。槩言在日本。则当从日本法律。为可云也。不愿剃发者不强。愿安心进饭。先生谓诸人曰。吾在司令部时曾闻。囚徒食费。自我政府担当云。故昨日两时之食。亦认以我政府徵来之物矣。且古人处义。有可据故耳。今彼云食日本之食。则当从日本之令。吾何可贪生糊口。以受食其食。不从其令之讥乎。吾事吾已断定。诸君则彼言既如此。岂可尽从我死乎。诸人迭进劝谏。皆不听。翌日。步兵队大将来问
与同事诸君默会。五绝诗十四首不拘帘格。信心叙实者存焉。吾当诵之。君还之日。分赠各人可也。仍呼小序曰。书生。无军旅之责。八十。非从戎之年。但值此非常之变。上自朝廷。下及草野。除喑聋跛躄外。其曰在家不知者。直是无人心者也。第孽由自作。累及诸君。惭负多矣。各赠五言一绝。用备日后掌故云。其一则自责也。林炳瓒,高石镇十二人。各有所赠。又其一哀郑时海也。是夕从先生不食者。林炳瓒,李侙,柳浚根,安恒植,南奎振。其馀五人。亦强进数匙而止。翌日队长来问曰。老人何故不食。炳瓒以日录示之曰。通辩未详。见此则可知矣。队长览毕曰。剃发云云。非指监禁人而言也。槩言在日本。则当从日本法律。为可云也。不愿剃发者不强。愿安心进饭。先生谓诸人曰。吾在司令部时曾闻。囚徒食费。自我政府担当云。故昨日两时之食。亦认以我政府徵来之物矣。且古人处义。有可据故耳。今彼云食日本之食。则当从日本之令。吾何可贪生糊口。以受食其食。不从其令之讥乎。吾事吾已断定。诸君则彼言既如此。岂可尽从我死乎。诸人迭进劝谏。皆不听。翌日。步兵队大将来问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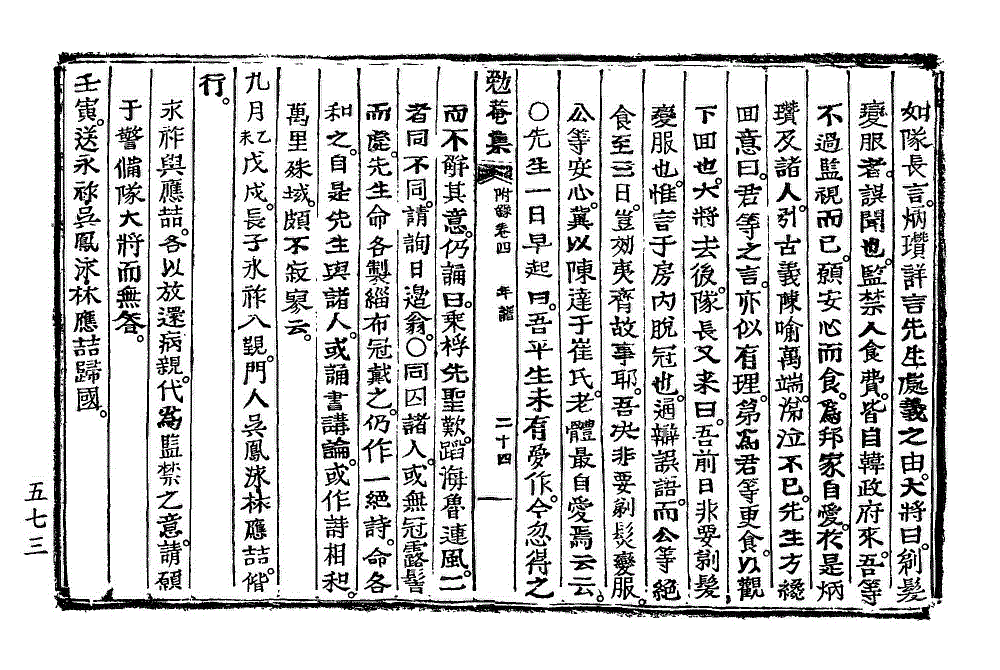 如队长言。炳瓒详言先生处义之由。大将曰。剃发变服者。误闻也。监禁人食费。皆自韩政府来。吾等不过监视而已。愿安心而食。为邦家自爱。于是炳瓒及诸人。引古义陈喻万端。涕泣不已。先生方才回意曰。君等之言。亦似有理。第为君等更食。以观下回也。大将去后。队长又来曰。吾前日非要剃发变服也。惟言于房内脱冠也。通辩误语。而公等绝食至三日。岂效夷齐故事耶。吾决非要剃发变服。公等安心。冀以陈达于崔氏。老体最自爱焉云云。○先生一日早起曰。吾平生未有梦作。今忽得之而不解其意。仍诵曰。乘桴先圣叹。蹈海鲁连风。二者同不同。请询日边翁。○同囚诸人。或无冠露髻而处。先生命各制缁布冠戴之。仍作一绝诗。命各和之。自是先生与诸人。或诵书讲论。或作诗相和。万里殊域。颇不寂寥云。
如队长言。炳瓒详言先生处义之由。大将曰。剃发变服者。误闻也。监禁人食费。皆自韩政府来。吾等不过监视而已。愿安心而食。为邦家自爱。于是炳瓒及诸人。引古义陈喻万端。涕泣不已。先生方才回意曰。君等之言。亦似有理。第为君等更食。以观下回也。大将去后。队长又来曰。吾前日非要剃发变服也。惟言于房内脱冠也。通辩误语。而公等绝食至三日。岂效夷齐故事耶。吾决非要剃发变服。公等安心。冀以陈达于崔氏。老体最自爱焉云云。○先生一日早起曰。吾平生未有梦作。今忽得之而不解其意。仍诵曰。乘桴先圣叹。蹈海鲁连风。二者同不同。请询日边翁。○同囚诸人。或无冠露髻而处。先生命各制缁布冠戴之。仍作一绝诗。命各和之。自是先生与诸人。或诵书讲论。或作诗相和。万里殊域。颇不寂寥云。九月(乙未)戊戌。长子永祚入觐。门人吴凤泳,林应哲。偕行。
永祚与应哲。各以放还病亲。代为监禁之意。请愿于警备队大将而无答。
壬寅。送永祚,吴凤泳,林应哲归国。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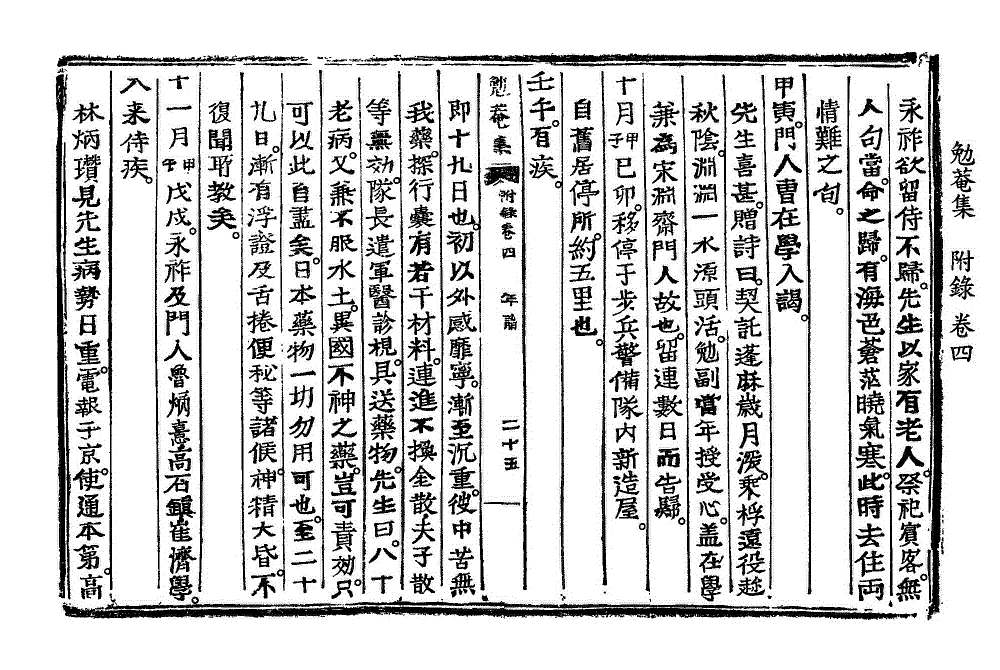 永祚欲留侍不归。先生以家有老人。祭祀宾客。无人句当。命之归。有海色苍茫晓气寒。此时去住两情难之句。
永祚欲留侍不归。先生以家有老人。祭祀宾客。无人句当。命之归。有海色苍茫晓气寒。此时去住两情难之句。甲寅。门人曹在学入谒。
先生喜甚。赠诗曰。契托蓬麻岁月深。乘桴远役趁秋阴。渊渊一水源头活。勉副当年授受心。盖在学兼为宋渊斋门人故也。留连数日而告归。
十月(甲子)己卯。移停于步兵警备队内新造屋。
自旧居停所。约五里也。
壬午。有疾。
即十九日也。初以外感靡宁。渐至沉重。彼中苦无我药。探行囊有若干材料。连进不换金散,夫子散等无效。队长遣军医诊视。具送药物。先生曰。八十老病。又兼不服水土。异国不神之药。岂可责效。只可以此自尽矣。日本药物一切勿用可也。至二十九日。渐有浮證及舌捲便秘等诸候。神精大昏。不复闻所教矣。
十一月(甲午)戊戌。永祚及门人鲁炳憙,高石镇,崔济学。入来侍疾。
林炳瓒见先生病势日重。电报于京。使通本第。高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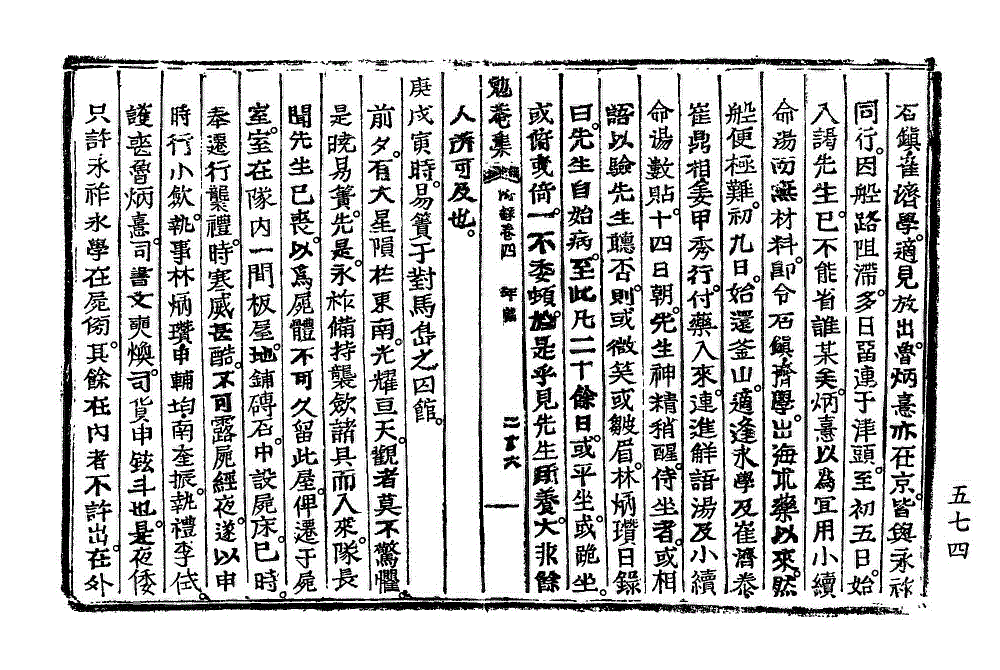 石镇,崔济学。适见放出。鲁炳憙亦在京。皆与永祚同行。因船路阻滞。多日留连于津头。至初五日。始入谒先生。已不能省谁某矣。炳憙以为宜用小续命汤而无材料。即令石镇,济学。出海求药以来。然船便极难。初九日。始还釜山。适逢永学及崔济泰,崔鼎相,姜甲秀行。付药入来。连进解语汤及小续命汤数贴。十四日朝。先生神精稍醒。侍坐者。或相语以验先生听否。则或微笑或皱眉。林炳瓒日录曰。先生自始病。至此凡二十馀日。或平坐。或跪坐。或俯或倚。一不委顿。于是乎见先生所养。大非馀人所可及也。
石镇,崔济学。适见放出。鲁炳憙亦在京。皆与永祚同行。因船路阻滞。多日留连于津头。至初五日。始入谒先生。已不能省谁某矣。炳憙以为宜用小续命汤而无材料。即令石镇,济学。出海求药以来。然船便极难。初九日。始还釜山。适逢永学及崔济泰,崔鼎相,姜甲秀行。付药入来。连进解语汤及小续命汤数贴。十四日朝。先生神精稍醒。侍坐者。或相语以验先生听否。则或微笑或皱眉。林炳瓒日录曰。先生自始病。至此凡二十馀日。或平坐。或跪坐。或俯或倚。一不委顿。于是乎见先生所养。大非馀人所可及也。庚戌寅时。易箦于对马岛之囚馆。
前夕。有大星陨于东南。光耀亘天。观者莫不惊惧。是晓易箦。先是。永祚备持袭敛诸具而入来。队长闻先生已丧。以为尸体不可久留此屋。俾迁于尸室。室在队内一间板屋。地铺砖石。中设尸床。巳时。奉迁行袭礼。时寒威甚酷。不可露尸经夜。遂以申时行小敛。执事林炳瓒,申辅均,南奎振。执礼李侙。护丧鲁炳憙。司书文奭焕。司货申铉斗也。是夜倭只许永祚,永学在尸傍。其馀在内者不许出。在外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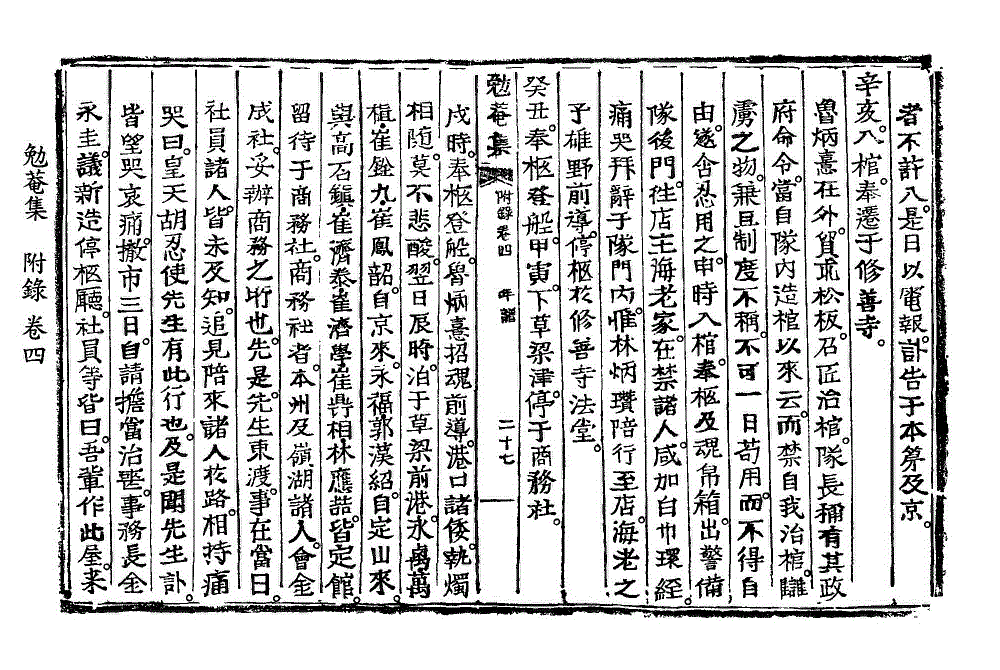 者不许入。是日以电报。讣告于本第及京。
者不许入。是日以电报。讣告于本第及京。辛亥。入棺。奉迁于修善寺。
鲁炳憙在外。贸求松板。召匠治棺。队长称有其政府命令。当自队内造棺以来云。而禁自我治棺。雠虏之物。兼且制度不称。不可一日苟用。而不得自由。遂含忍用之。申时入棺。奉柩及魂帛箱。出警备队后门。往店主海老家。在禁诸人。咸加白巾环绖。痛哭拜辞于队门内。惟林炳瓒陪行至店。海老之子雄野前导。停柩于修善寺法堂。
癸丑。奉柩登船。甲寅。下草梁津。停于商务社。
戌时。奉柩登船。鲁炳憙招魂前导。港口诸倭。执烛相随。莫不悲酸。翌日辰时。泊于草梁前港。永卨,万植,崔铨九,崔凤韶。自京来。永福,郭汉绍。自定山来。与高石镇,崔济泰,崔济学,崔鼎相,林应哲。皆定馆。留待于商务社。商务社者。本州及岭湖诸人。会金成社。妥办商务之所也。先是。先生东渡。事在当日。社员诸人。皆未及知。追见陪来诸人于路。相持痛哭曰。皇天胡忍使先生有此行也。及是闻先生讣。皆望哭哀痛。撤市三日。自请担当治丧。事务长金永圭。议新造停柩厅。社员等皆曰。吾辈作此屋。来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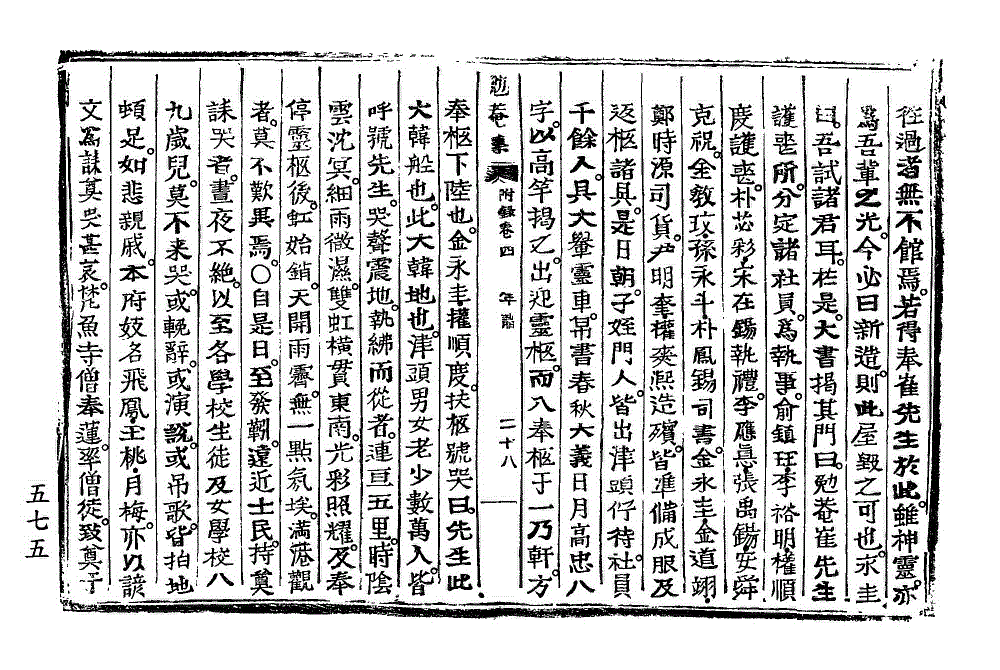 往过者无不馆焉。若得奉崔先生于此。虽神灵。亦为吾辈之光。今必曰新造。则此屋毁之可也。永圭曰。吾试诸君耳。于是。大书揭其门曰。勉庵崔先生护丧所。分定诸社员。为执事。俞镇珏,李裕明,权顺度护丧。朴苾彩,宋在锡执礼。李应德,张禹锡,安舜克祝。金教玟,孙永斗,朴凤锡司书。金永圭,金道翊,郑时源司货。尹明奎,权爽熙造殡。皆准备成服及返柩诸具。是日朝。子侄门人。皆出津头伫待。社员千馀人。具大舆灵车。帛书春秋大义日月高忠八字。以高竿揭之。出迎灵柩。而入奉柩于一乃轩。方奉柩下陆也。金永圭,权顺度。扶柩号哭曰。先生此大韩船也。此大韩地也。津头男女老少数万人。皆呼号先生。哭声震地。执绋而从者。连亘五里。时阴云沈冥。细雨微湿。双虹横贯东南。光彩照耀。及奉停灵柩后。虹始销。天开雨霁。无一点氛埃。满港观者。莫不叹异焉。○自是日。至发靷。远近士民。持奠诔哭者。昼夜不绝。以至各学校生徒及女学校八九岁儿。莫不来哭。或挽辞。或演说。或吊歌。皆拍地顿足。如悲亲戚。本府妓名飞凤,玉桃,月梅。亦以谚文为诔奠哭甚哀。梵鱼寺僧奉莲。率僧徒。致奠于
往过者无不馆焉。若得奉崔先生于此。虽神灵。亦为吾辈之光。今必曰新造。则此屋毁之可也。永圭曰。吾试诸君耳。于是。大书揭其门曰。勉庵崔先生护丧所。分定诸社员。为执事。俞镇珏,李裕明,权顺度护丧。朴苾彩,宋在锡执礼。李应德,张禹锡,安舜克祝。金教玟,孙永斗,朴凤锡司书。金永圭,金道翊,郑时源司货。尹明奎,权爽熙造殡。皆准备成服及返柩诸具。是日朝。子侄门人。皆出津头伫待。社员千馀人。具大舆灵车。帛书春秋大义日月高忠八字。以高竿揭之。出迎灵柩。而入奉柩于一乃轩。方奉柩下陆也。金永圭,权顺度。扶柩号哭曰。先生此大韩船也。此大韩地也。津头男女老少数万人。皆呼号先生。哭声震地。执绋而从者。连亘五里。时阴云沈冥。细雨微湿。双虹横贯东南。光彩照耀。及奉停灵柩后。虹始销。天开雨霁。无一点氛埃。满港观者。莫不叹异焉。○自是日。至发靷。远近士民。持奠诔哭者。昼夜不绝。以至各学校生徒及女学校八九岁儿。莫不来哭。或挽辞。或演说。或吊歌。皆拍地顿足。如悲亲戚。本府妓名飞凤,玉桃,月梅。亦以谚文为诔奠哭甚哀。梵鱼寺僧奉莲。率僧徒。致奠于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6H 页
 路傍。草梁三寡妇。自津头陪舆哭从。及至龟浦。头戴奠物。徒步四十里而来曰。大监祭需。不可载于倭车。器皿亦不敢用倭物云。
路傍。草梁三寡妇。自津头陪舆哭从。及至龟浦。头戴奠物。徒步四十里而来曰。大监祭需。不可载于倭车。器皿亦不敢用倭物云。乙卯。成服。
远近士民男女来哭者。数万人。外国人来观者。亦皆流泪被面云。
丙辰。发靷。
大舆灵车。担夫。皆自商务社专担。自草梁至龟浦。凡四十里内。靷而从者愈众。家家皆插白幡。所过妇女。皆哭。迎祭路上者。又相续。是日仅行十里。次日行三十里。至龟浦。此是东莱尽境也。商社诸人至此。皆辞哭失声。然后归。俞镇珏。始终护丧。至定山而返。○先生始丧严原。警备队长致赙钱二百缗。永祚屡却之。队长怒。有沮戏渡海之言。不得已受而藏之。至发靷日。以邮递还送。
十二月(癸亥)己巳。至定山本第。壬申大敛。改棺。乙亥。殡。
渡龟浦江。历金海,昌原,漆原,昌宁,玄风,星州,开宁,金山,黄涧,永同,沃川,怀德,公州。首尾十五日。始抵定山。本第。所过州郡。持奠来哭者。一如东莱。(昌宁人朴芝林。即一农夫。而犹慕先生。致奠致赙。哭甚哀。)虽平日异论之人。亦莫不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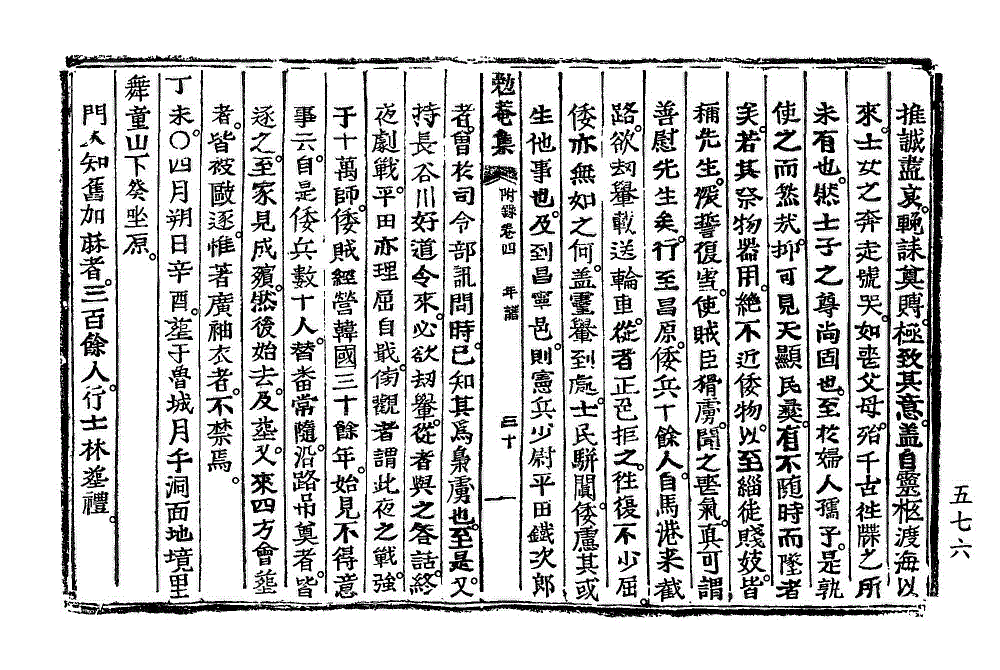 推诚尽哀。挽诔奠赙。极致其意。盖自灵柩渡海以来。士女之奔走号哭。如丧父母。殆千古往牒之所未有也。然士子之尊尚固也。至于妇人孺子。是孰使之而然哉。抑可见天显民彝。有不随时而坠者矣。若其祭物器用。绝不近倭物。以至缁徒贱妓。皆称先生。深誓复雪。使贼臣猾虏。闻之丧气。真可谓善慰先生矣。行至昌原。倭兵十馀人。自马港来截路。欲劫舆载送轮车。从者正色拒之。往复不少屈。倭亦无如之何。盖灵舆到处。士民骈阗。倭虑其或生他事也。及到昌宁邑。则宪兵少尉平田铁次郎者。曾于司令部讯问时。已知其为枭虏也。至是。又持长谷川好道令来。必欲劫舆。从者与之答话。终夜剧战。平田亦理屈自戢。傍观者谓此夜之战。强于十万师。倭贼经营韩国三十馀年。始见不得意事云。自是倭兵数十人。替番常随。沿路吊奠者。皆逐之。至家见成殡。然后始去。及葬。又来四方会葬者。皆被驱逐。惟著广袖衣者。不禁焉。
推诚尽哀。挽诔奠赙。极致其意。盖自灵柩渡海以来。士女之奔走号哭。如丧父母。殆千古往牒之所未有也。然士子之尊尚固也。至于妇人孺子。是孰使之而然哉。抑可见天显民彝。有不随时而坠者矣。若其祭物器用。绝不近倭物。以至缁徒贱妓。皆称先生。深誓复雪。使贼臣猾虏。闻之丧气。真可谓善慰先生矣。行至昌原。倭兵十馀人。自马港来截路。欲劫舆载送轮车。从者正色拒之。往复不少屈。倭亦无如之何。盖灵舆到处。士民骈阗。倭虑其或生他事也。及到昌宁邑。则宪兵少尉平田铁次郎者。曾于司令部讯问时。已知其为枭虏也。至是。又持长谷川好道令来。必欲劫舆。从者与之答话。终夜剧战。平田亦理屈自戢。傍观者谓此夜之战。强于十万师。倭贼经营韩国三十馀年。始见不得意事云。自是倭兵数十人。替番常随。沿路吊奠者。皆逐之。至家见成殡。然后始去。及葬。又来四方会葬者。皆被驱逐。惟著广袖衣者。不禁焉。丁未。○四月朔日辛酉。葬于鲁城月午洞面地境里舞童山下癸坐原。
门人知旧加麻者。三百馀人。行士林葬礼。
勉庵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 第 5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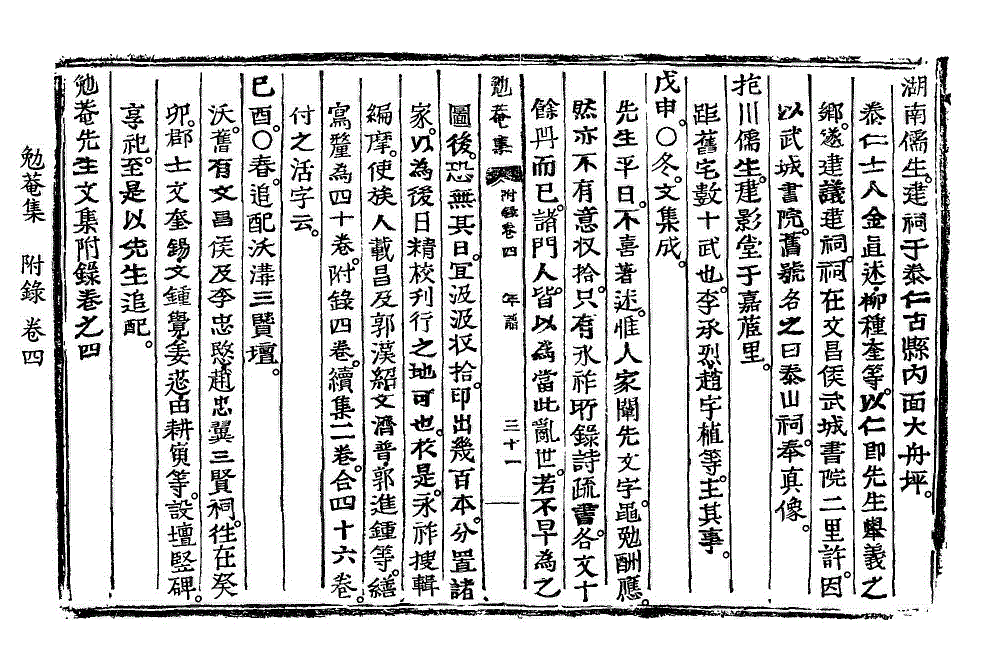 湖南儒生。建祠于泰仁古县内面大舟坪。
湖南儒生。建祠于泰仁古县内面大舟坪。泰仁士人金直述,柳种奎等。以仁即先生举义之乡。遂建议建祠。祠在文昌倭武城书院二里许。因以武城书院。旧号名之曰泰山祠。奉真像。
抱川儒生。建影堂于嘉茝里。
距旧宅数十武也。李承烈,赵宇植等。主其事。
戊申。○冬。文集成。
先生平日。不喜著述。惟人家阐先文字。黾勉酬应。然亦不有意收拾。只有永祚所录诗疏书。各文十馀册而已。诸门人。皆以为当此乱世。若不早为之图后。恐无其日。宜汲汲收拾。印出几百本。分置诸家。以为后日精校刊行之地可也。于是。永祚搜辑编摩。使族人载昌及郭汉绍,文济普,郭进钟等。缮写釐为四十卷。附录四卷。续集二卷。合四十六卷。付之活字云。
己酉。○春。追配沃沟三贤坛。
沃。旧有文昌侯及李忠悯,赵忠翼三贤祠。往在癸卯。郡士文奎锡,文钟觉,姜莚,田耕寅等。设坛竖碑。享祀。至是以先生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