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x 页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讲说杂稿
讲说杂稿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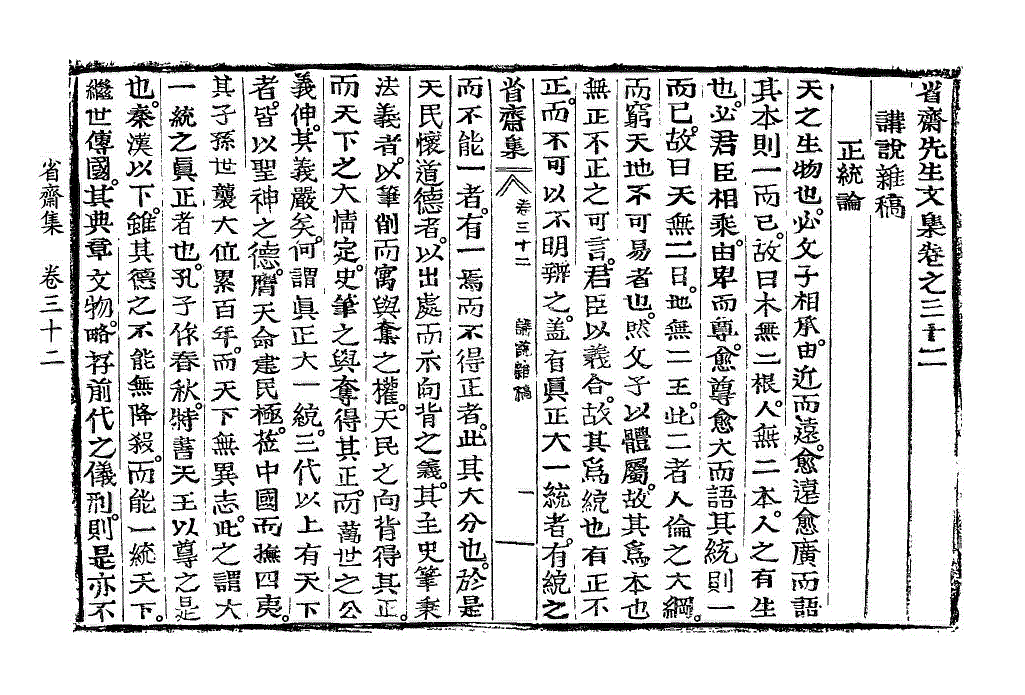 正统论
正统论天之生物也。必父子相承。由近而远。愈远愈广而语其本则一而已。故曰木无二根。人无二本。人之有生也。必君臣相乘。由卑而尊。愈尊愈大而语其统则一而已。故曰天无二日。地无二王。此二者人伦之大纲。而穷天地不可易者也。然父子以体属。故其为本也无正不正之可言。君臣以义合。故其为统也有正不正。而不可以不明辨之。盖有真正大一统者。有统之而不能一者。有一焉而不得正者。此其大分也。于是天民怀道德者。以出处而示向背之义。其主史笔秉法义者。以笔削而寓与夺之权。天民之向背得其正。而天下之大情定。史笔之与夺得其正。而万世之公义伸。其义严矣。何谓真正大一统。三代以上有天下者。皆以圣神之德。膺天命建民极。莅中国而抚四夷。其子孙世袭大位累百年。而天下无异志。此之谓大一统之真正者也。孔子作春秋。特书天王以尊之是也。秦汉以下。虽其德之不能无降杀。而能一统天下。继世传国。其典章文物。略存前代之仪刑。则是亦不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5L 页
 失为正统也。故仁人君子之生于其世者。不以名义而疑所事。朱子继春秋修纲目。大书纪年。称帝书崩以尊之矣。何谓统之而不能一。如六朝五季分治之君。及汉唐创业之主。未及混一天下之时是也。于其中名义有正有不正。生于其世者。择而事之。无不可。惟秉史笔者。一以无统之例处之。纲目之注年。称主书殂是也。若是正统之末。为乱贼所割据。夷狄所侵夺而不能一者。虽削弱琐尾之甚。自当以正统尊之。而彼割据而侵夺者。在所必讨。故仕其朝者益露其节。而书之策者益彰其义。如东周蜀汉东晋之类是也。何谓一焉而不得正。乱贼之窃居大位。夷狄之冒据中国。其统之非不一矣。而断之以名义。则伪而非真。僭而不正也。然乱贼之干统。屡见于前代。故朱子悉得正其法。如汉王莽唐武后之类是也。惟夷狄干统之变。晚出于胡元以后。而我宋子继孔朱明大义。盖黜许衡于夫子庙庭。而凡以儒名失身于秽朝者。皆知所惧矣。大书妥欢贴睦尔五年于金石显刻。而后之秉史笔删伪号者。得有所据矣。至于所值清处之世。则其处之益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垂三百年。犹以 皇明旧君为
失为正统也。故仁人君子之生于其世者。不以名义而疑所事。朱子继春秋修纲目。大书纪年。称帝书崩以尊之矣。何谓统之而不能一。如六朝五季分治之君。及汉唐创业之主。未及混一天下之时是也。于其中名义有正有不正。生于其世者。择而事之。无不可。惟秉史笔者。一以无统之例处之。纲目之注年。称主书殂是也。若是正统之末。为乱贼所割据。夷狄所侵夺而不能一者。虽削弱琐尾之甚。自当以正统尊之。而彼割据而侵夺者。在所必讨。故仕其朝者益露其节。而书之策者益彰其义。如东周蜀汉东晋之类是也。何谓一焉而不得正。乱贼之窃居大位。夷狄之冒据中国。其统之非不一矣。而断之以名义。则伪而非真。僭而不正也。然乱贼之干统。屡见于前代。故朱子悉得正其法。如汉王莽唐武后之类是也。惟夷狄干统之变。晚出于胡元以后。而我宋子继孔朱明大义。盖黜许衡于夫子庙庭。而凡以儒名失身于秽朝者。皆知所惧矣。大书妥欢贴睦尔五年于金石显刻。而后之秉史笔删伪号者。得有所据矣。至于所值清处之世。则其处之益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垂三百年。犹以 皇明旧君为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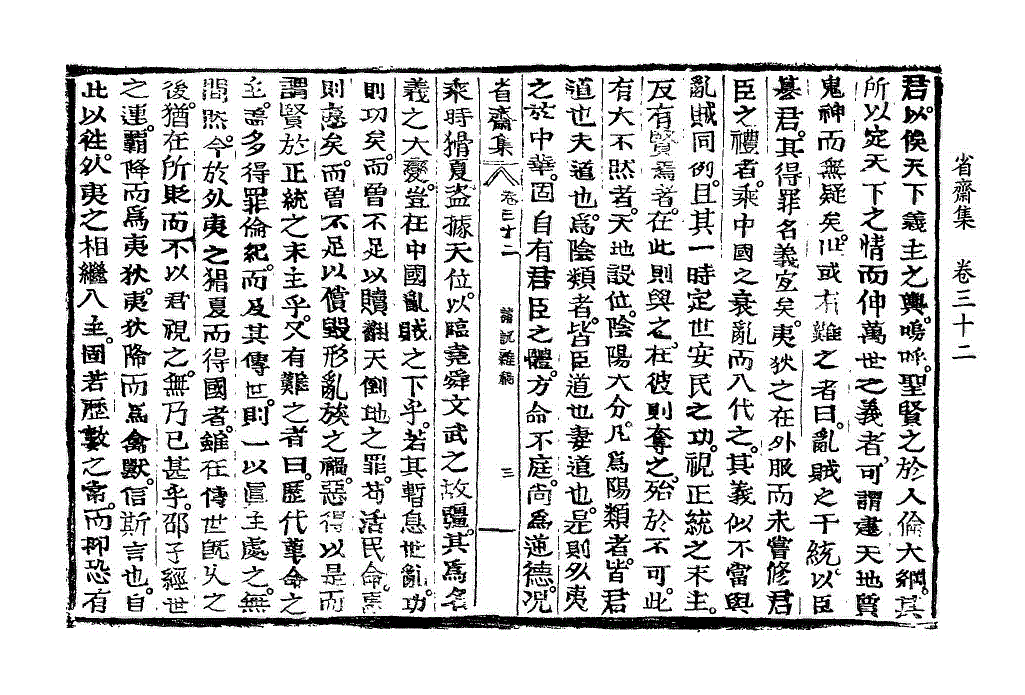 君。以俟天下义主之舆。呜呼。圣贤之于人伦大纲。其所以定天下之情而伸万世之义者。可谓建天地质鬼神而无疑矣。世或有难之者曰。乱贼之干统。以臣篡君。其得罪名义宜矣。夷狄之在外服而未尝修君臣之礼者。乘中国之衰乱而入代之。其义似不当与乱贼同例。且其一时定世安民之功。视正统之末主。反有贤焉者。在此则与之。在彼则夺之。殆于不可。此有大不然者。天地设位。阴阳大分。凡为阳类者。皆君道也夫道也。为阴类者。皆臣道也妻道也。是则外夷之于中华。固自有君臣之体。方命不庭。尚为逆德。况乘时猾夏。盗据天位。以临尧舜文武之故疆。其为名义之大变。岂在中国乱贼之下乎。若其暂息世乱。功则功矣。而曾不足以赎翻天倒地之罪。苟活民命。惠则惠矣。而曾不足以偿毁形乱族之祸。恶得以是而谓贤于正统之末主乎。又有难之者曰。历代革命之主。盖多得罪伦纪。而及其传世。则一以真主处之。无间然。今于外夷之猾夏而得国者。虽在传世既久之后。犹在所贬而不以君视之。无乃已甚乎。邵子经世之连。霸降而为夷狄。夷狄降而为禽兽。信斯言也。自此以往。外夷之相继入主。固若历数之常。而抑恐有
君。以俟天下义主之舆。呜呼。圣贤之于人伦大纲。其所以定天下之情而伸万世之义者。可谓建天地质鬼神而无疑矣。世或有难之者曰。乱贼之干统。以臣篡君。其得罪名义宜矣。夷狄之在外服而未尝修君臣之礼者。乘中国之衰乱而入代之。其义似不当与乱贼同例。且其一时定世安民之功。视正统之末主。反有贤焉者。在此则与之。在彼则夺之。殆于不可。此有大不然者。天地设位。阴阳大分。凡为阳类者。皆君道也夫道也。为阴类者。皆臣道也妻道也。是则外夷之于中华。固自有君臣之体。方命不庭。尚为逆德。况乘时猾夏。盗据天位。以临尧舜文武之故疆。其为名义之大变。岂在中国乱贼之下乎。若其暂息世乱。功则功矣。而曾不足以赎翻天倒地之罪。苟活民命。惠则惠矣。而曾不足以偿毁形乱族之祸。恶得以是而谓贤于正统之末主乎。又有难之者曰。历代革命之主。盖多得罪伦纪。而及其传世。则一以真主处之。无间然。今于外夷之猾夏而得国者。虽在传世既久之后。犹在所贬而不以君视之。无乃已甚乎。邵子经世之连。霸降而为夷狄。夷狄降而为禽兽。信斯言也。自此以往。外夷之相继入主。固若历数之常。而抑恐有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6L 页
 甚于此者。是岂可尽以变例处之乎。此亦有不然者。中国之革命而犯罪者。罪止其身。外夷之干统而传国者。世袭其陋。安得以一例处之。若为夷主之子孙者。能一洗夷陋。以从中华之典章文物。则是亦华而已矣。岂复有贬抑乎。夷运长短。诚有不可知者。然天下之理。不以成败而论得失。不以众寡而决正邪。不以久暂而定常变。华夷阴阳之分。顺逆正倒之体。岂以种类多少运数长短而有改易哉。政惟接踵于方来者。有无穷之忧。所以定名于既往者。不得不致慎也。呜呼。天地之正理。明如日星。而流俗之浅见。日就乎昏濛。圣贤之大训。严于斧钺。而处士之横议。苦欲其变乱。吾不知此何气候也。独不观夫百物之情乎。野花向日而开。暝至则阖。暝至而不知阖者。必将落之花也。土虫闻雷而动。凉至则蛰。凉至而不知蛰者。必将死之虫也。其故何也。失其向背之恒性也。惟人万物之灵。惟士万夫之望。目见太阳之薄蚀于中天。而指以为大明。身值寒威之严凝于九野。而就之如阳春。既失其恒性。又思以易天下。纵玆以往。不惟大一统之无期可复。并与一本生生之理而或几乎息矣。吾为此惧。作正统论。以效孟津之一捧土。
甚于此者。是岂可尽以变例处之乎。此亦有不然者。中国之革命而犯罪者。罪止其身。外夷之干统而传国者。世袭其陋。安得以一例处之。若为夷主之子孙者。能一洗夷陋。以从中华之典章文物。则是亦华而已矣。岂复有贬抑乎。夷运长短。诚有不可知者。然天下之理。不以成败而论得失。不以众寡而决正邪。不以久暂而定常变。华夷阴阳之分。顺逆正倒之体。岂以种类多少运数长短而有改易哉。政惟接踵于方来者。有无穷之忧。所以定名于既往者。不得不致慎也。呜呼。天地之正理。明如日星。而流俗之浅见。日就乎昏濛。圣贤之大训。严于斧钺。而处士之横议。苦欲其变乱。吾不知此何气候也。独不观夫百物之情乎。野花向日而开。暝至则阖。暝至而不知阖者。必将落之花也。土虫闻雷而动。凉至则蛰。凉至而不知蛰者。必将死之虫也。其故何也。失其向背之恒性也。惟人万物之灵。惟士万夫之望。目见太阳之薄蚀于中天。而指以为大明。身值寒威之严凝于九野。而就之如阳春。既失其恒性。又思以易天下。纵玆以往。不惟大一统之无期可复。并与一本生生之理而或几乎息矣。吾为此惧。作正统论。以效孟津之一捧土。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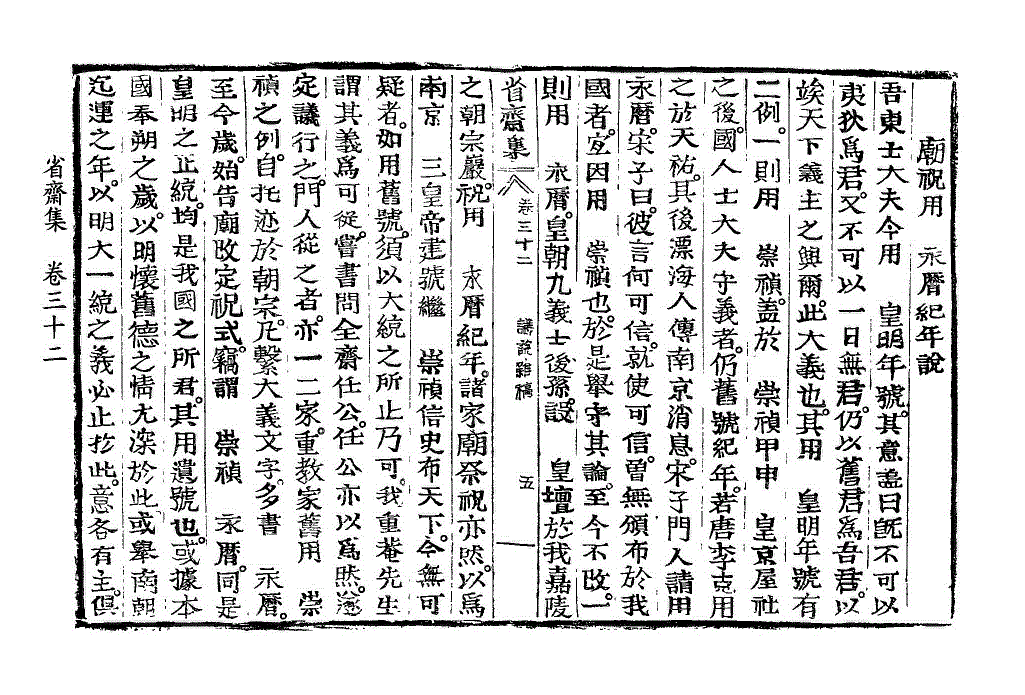 庙祝用 永历纪年说
庙祝用 永历纪年说吾东士大夫今用 皇明年号。其意盖曰既不可以夷狄为君。又不可以一日无君。仍以旧君为吾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尔。此大义也。其用 皇明年号有二例。一则用 崇祯。盖于 崇祯甲申 皇京屋社之后。国人士大夫守义者。仍旧号纪年。若唐李克用之于天祐。其后漂海人传南京消息。宋子门人请用永历。宋子曰。彼言何可信。就使可信。曾无颁布于我国者。宜因用 崇祯也。于是举守其论。至今不改。一则用 永历。皇朝九义士后孙。设 皇坛于我嘉陵之朝宗岩。祝用 永历纪年。诸家庙祭祝亦然。以为南京 三皇帝建号继 崇祯信史布天下。今无可疑者。如用旧号。须以大统之所止乃可。我重庵先生谓其义为可从。尝书问全斋任公。任公亦以为然。遂定议行之。门人从之者。亦一二家。重教家旧用 崇祯之例。自托迹于朝宗。凡系大义文字。多书 永历。至今岁。始告庙改定祝式。窃谓 崇祯 永历。同是皇明之正统。均是我国之所君。其用遗号也。或据本国奉朔之岁。以明怀旧德之情尤深于此。或举南朝迄运之年。以明大一统之义必止于此。意各有主。俱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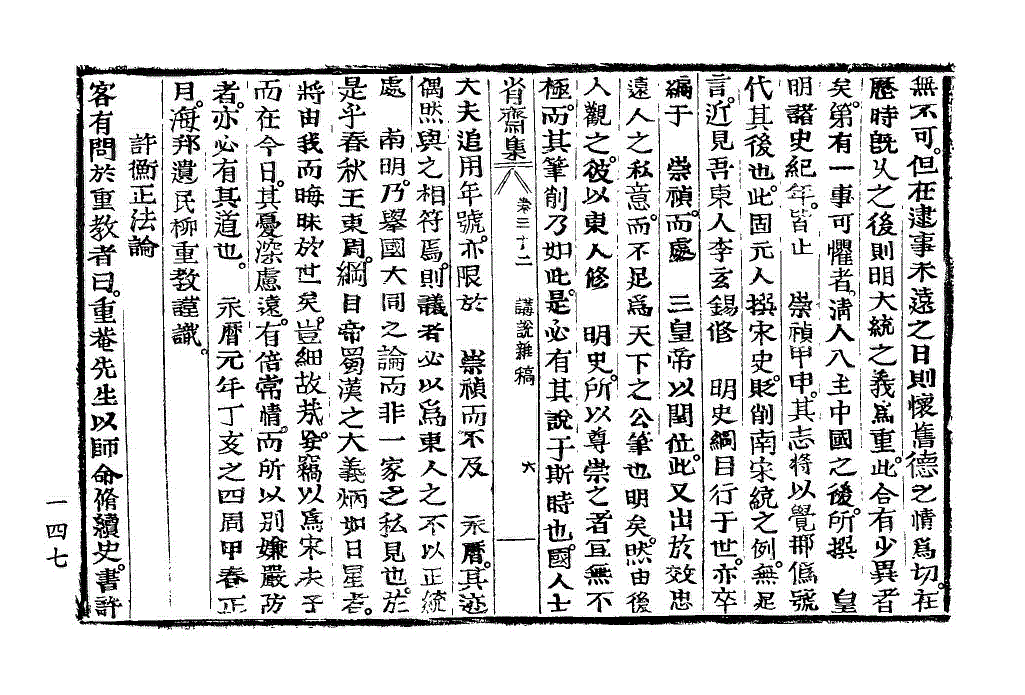 无不可。但在逮事未远之日则怀旧德之情为切。在历时既久之后则明大统之义为重。此合有少异者矣。第有一事可惧者。清人入主中国之后。所撰 皇明诸史纪年。皆止 崇祯甲申。其志将以觉那伪号代其后也。此固元人撰宋史。贬削南宋统之例。无足言。近见吾东人李玄锡修 明史纲目行于世。亦卒编于 崇祯。而处 三皇帝以闰位。此又出于效忠远人之私意。而不足为天下之公笔也明矣。然由后人观之。彼以东人修 明史。所以尊崇之者宜无不极。而其笔削乃如此。是必有其说于斯时也。国人士大夫追用年号。亦限于 崇祯而不及 永历。其迹偶然与之相符焉。则议者必以为东人之不以正统处 南明。乃举国大同之论而非一家之私见也。于是乎春秋王东周。纲目帝蜀汉之大义炳如日星者。将由我而晦昧于世矣。岂细故哉。妄窃以为宋夫子而在今日。其忧深虑远。有倍常情。而所以别嫌严防者。亦必有其道也。 永历元年丁亥之四周甲春正月。海邦遗民柳重教谨识。
无不可。但在逮事未远之日则怀旧德之情为切。在历时既久之后则明大统之义为重。此合有少异者矣。第有一事可惧者。清人入主中国之后。所撰 皇明诸史纪年。皆止 崇祯甲申。其志将以觉那伪号代其后也。此固元人撰宋史。贬削南宋统之例。无足言。近见吾东人李玄锡修 明史纲目行于世。亦卒编于 崇祯。而处 三皇帝以闰位。此又出于效忠远人之私意。而不足为天下之公笔也明矣。然由后人观之。彼以东人修 明史。所以尊崇之者宜无不极。而其笔削乃如此。是必有其说于斯时也。国人士大夫追用年号。亦限于 崇祯而不及 永历。其迹偶然与之相符焉。则议者必以为东人之不以正统处 南明。乃举国大同之论而非一家之私见也。于是乎春秋王东周。纲目帝蜀汉之大义炳如日星者。将由我而晦昧于世矣。岂细故哉。妄窃以为宋夫子而在今日。其忧深虑远。有倍常情。而所以别嫌严防者。亦必有其道也。 永历元年丁亥之四周甲春正月。海邦遗民柳重教谨识。许衡正法论
客有问于重教者曰。重庵先生以师命脩续史。书许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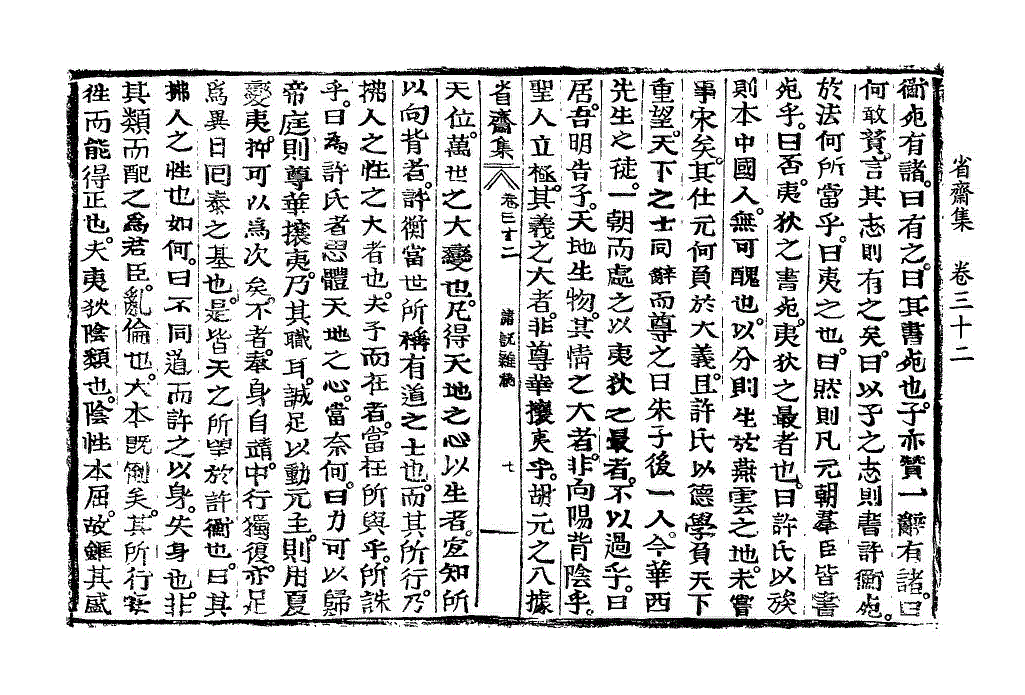 衡死有诸。曰有之。曰其书死也。子亦赞一辞有诸。曰何敢赞。言其志则有之矣。曰以子之志则书许衡死。于法何所当乎。曰夷之也。曰然则凡元朝群臣皆书死乎。曰否。夷狄之书死。夷狄之最者也。曰许氏以族则本中国人。无可丑也。以分则生于燕云之地。未尝事宋矣。其仕元何负于大义。且许氏以德学负天下重望。天下之士同辞而尊之曰朱子后一人。今华西先生之徒。一朝而处之以夷狄之最者。不以过乎。曰居。吾明告子。天地生物。其情之大者。非向阳背阴乎。圣人立极。其义之大者。非尊华攘夷乎。胡元之入据天位。万世之大变也。凡得天地之心以生者。宜知所以向背者。许衡当世所称有道之士也。而其所行。乃拂人之性之大者也。夫子而在者。当在所与乎。所诛乎。曰为许氏者思体天地之心。当奈何。曰力可以归帝庭。则尊华攘夷。乃其职耳。诚足以动元主。则用夏变夷。抑可以为次矣。不者。奉身自靖。中行独复。亦足为异日回泰之基也。是皆天之所望于许衡也。曰其拂人之性也如何。曰不同道而许之以身。失身也。非其类而配之为君臣。乱伦也。大本既倒矣。其所行安往而能得正也。夫夷狄阴类也。阴性本屈。故虽其盛
衡死有诸。曰有之。曰其书死也。子亦赞一辞有诸。曰何敢赞。言其志则有之矣。曰以子之志则书许衡死。于法何所当乎。曰夷之也。曰然则凡元朝群臣皆书死乎。曰否。夷狄之书死。夷狄之最者也。曰许氏以族则本中国人。无可丑也。以分则生于燕云之地。未尝事宋矣。其仕元何负于大义。且许氏以德学负天下重望。天下之士同辞而尊之曰朱子后一人。今华西先生之徒。一朝而处之以夷狄之最者。不以过乎。曰居。吾明告子。天地生物。其情之大者。非向阳背阴乎。圣人立极。其义之大者。非尊华攘夷乎。胡元之入据天位。万世之大变也。凡得天地之心以生者。宜知所以向背者。许衡当世所称有道之士也。而其所行。乃拂人之性之大者也。夫子而在者。当在所与乎。所诛乎。曰为许氏者思体天地之心。当奈何。曰力可以归帝庭。则尊华攘夷。乃其职耳。诚足以动元主。则用夏变夷。抑可以为次矣。不者。奉身自靖。中行独复。亦足为异日回泰之基也。是皆天之所望于许衡也。曰其拂人之性也如何。曰不同道而许之以身。失身也。非其类而配之为君臣。乱伦也。大本既倒矣。其所行安往而能得正也。夫夷狄阴类也。阴性本屈。故虽其盛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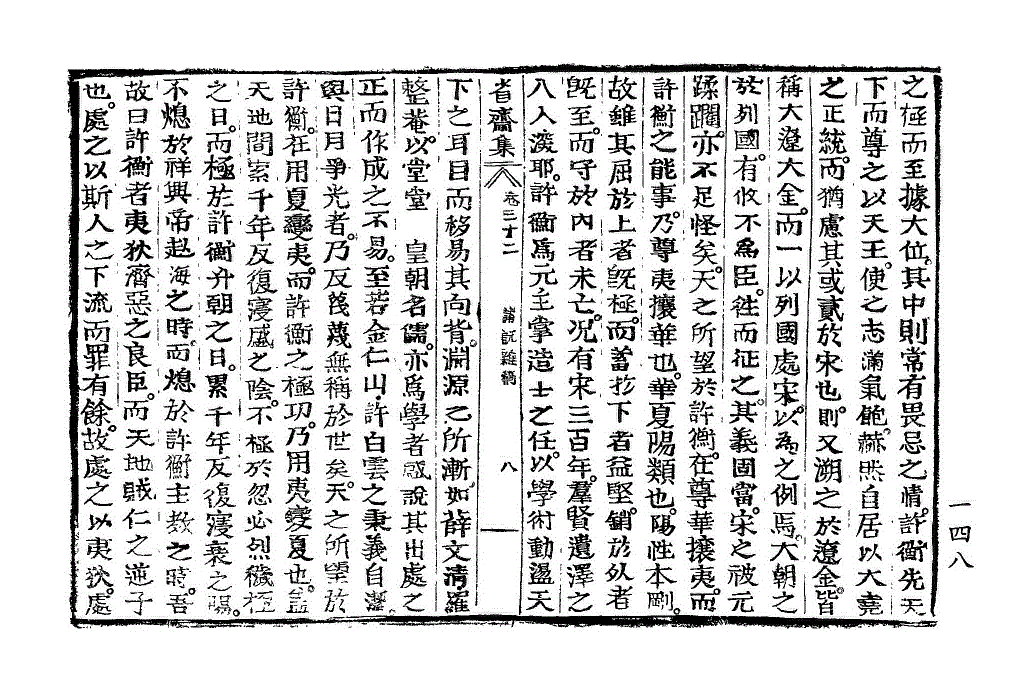 之极而至据大位。其中则常有畏忌之情。许衡先天下而尊之以天王。使之志满气饱。赫然自居以大尧之正统。而犹虑其或贰于宋也。则又溯之于辽金。皆称大辽大金。而一以列国处宋。以为之例焉。大朝之于列国。有攸不为臣。往而征之。其义固当。宋之被元蹂躏。亦不足怪矣。天之所望于许衡。在尊华攘夷。而许衡之能事。乃尊夷攘华也。华夏阳类也。阳性本刚。故虽其屈于上者既极。而蓄于下者益坚。销于外者既至。而守于内者未亡。况有宋三百年。群贤遗泽之入人深耶。许衡为元主掌造士之任。以学术动荡天下之耳目而移易其向背。渊源之所渐。如薛文清,罗整庵。以堂堂 皇朝名儒。亦为学者盛说其出处之正而作成之不易。至若金仁山,许白云之秉义自洁。与日月争光者。乃反蔑蔑无称于世矣。天之所望于许衡。在用夏变夷。而许衡之极功。乃用夷变夏也。盖天地间索千年反复寖盛之阴。不极于忽必烈秽极之日。而极于许衡升朝之日。累千年反复寖衰之阳。不熄于祥兴帝赴海之时。而熄于许衡主教之时。吾故曰许衡者夷狄济恶之良臣。而天地贼仁之逆子也。处之以斯人之下流而罪有馀。故处之以夷狄。处
之极而至据大位。其中则常有畏忌之情。许衡先天下而尊之以天王。使之志满气饱。赫然自居以大尧之正统。而犹虑其或贰于宋也。则又溯之于辽金。皆称大辽大金。而一以列国处宋。以为之例焉。大朝之于列国。有攸不为臣。往而征之。其义固当。宋之被元蹂躏。亦不足怪矣。天之所望于许衡。在尊华攘夷。而许衡之能事。乃尊夷攘华也。华夏阳类也。阳性本刚。故虽其屈于上者既极。而蓄于下者益坚。销于外者既至。而守于内者未亡。况有宋三百年。群贤遗泽之入人深耶。许衡为元主掌造士之任。以学术动荡天下之耳目而移易其向背。渊源之所渐。如薛文清,罗整庵。以堂堂 皇朝名儒。亦为学者盛说其出处之正而作成之不易。至若金仁山,许白云之秉义自洁。与日月争光者。乃反蔑蔑无称于世矣。天之所望于许衡。在用夏变夷。而许衡之极功。乃用夷变夏也。盖天地间索千年反复寖盛之阴。不极于忽必烈秽极之日。而极于许衡升朝之日。累千年反复寖衰之阳。不熄于祥兴帝赴海之时。而熄于许衡主教之时。吾故曰许衡者夷狄济恶之良臣。而天地贼仁之逆子也。处之以斯人之下流而罪有馀。故处之以夷狄。处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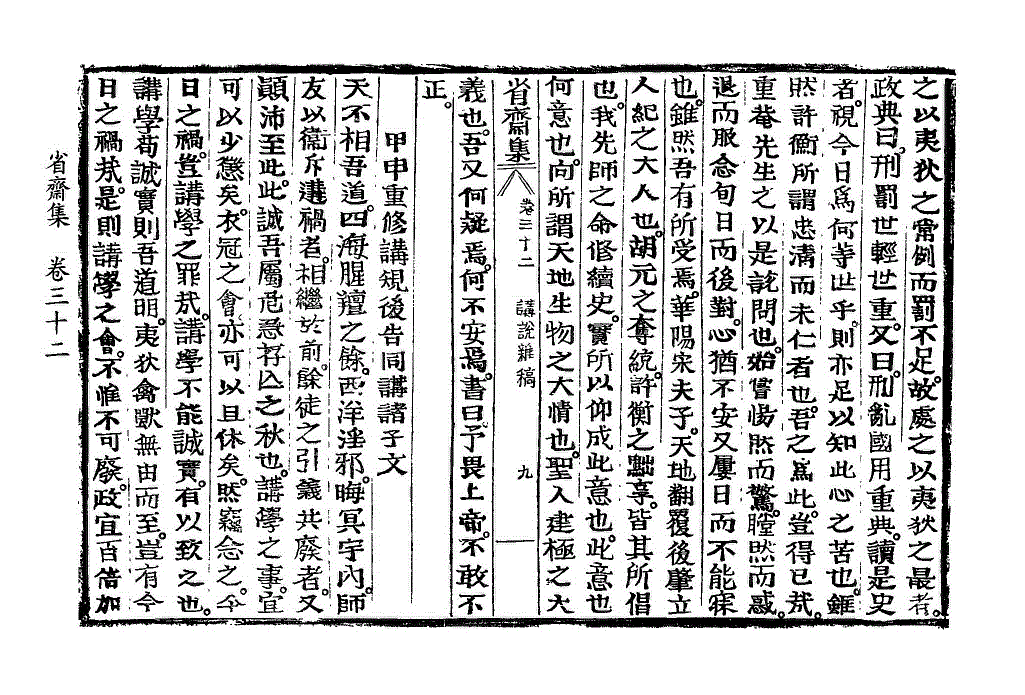 之以夷狄之常例而罚不足。故处之以夷狄之最者。政典曰。刑罚世轻世重。又曰。刑乱国用重典。读是史者。视今日为何等世乎。则亦足以知此心之苦也。虽然许衡所谓忠清而未仁者也。吾之为此。岂得已哉。重庵先生之以是说问也。始尝惕然而惊。瞠然而惑。退而服念旬日而后对。心犹不安又屡日而不能寐也。虽然吾有所受焉。华阳宋夫子。天地翻覆后肇立人纪之大人也。胡元之夺统。许衡之黜享。皆其所倡也。我先师之命修续史。实所以仰成此意也。此意也何意也。向所谓天地生物之大情也。圣人建极之大义也。吾又何疑焉。何不安焉。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之以夷狄之常例而罚不足。故处之以夷狄之最者。政典曰。刑罚世轻世重。又曰。刑乱国用重典。读是史者。视今日为何等世乎。则亦足以知此心之苦也。虽然许衡所谓忠清而未仁者也。吾之为此。岂得已哉。重庵先生之以是说问也。始尝惕然而惊。瞠然而惑。退而服念旬日而后对。心犹不安又屡日而不能寐也。虽然吾有所受焉。华阳宋夫子。天地翻覆后肇立人纪之大人也。胡元之夺统。许衡之黜享。皆其所倡也。我先师之命修续史。实所以仰成此意也。此意也何意也。向所谓天地生物之大情也。圣人建极之大义也。吾又何疑焉。何不安焉。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甲申重修讲规后告同讲诸子文
天不相吾道。四海腥膻之馀。西洋淫邪。晦冥宇内。师友以卫斥遘祸者。相继于前。馀徒之引义共废者。又颠沛至此。此诚吾属危急存亡之秋也。讲学之事。宜可以少惩矣。衣冠之会。亦可以且休矣。然窃念之。今日之祸。岂讲学之罪哉。讲学不能诚实。有以致之也。讲学苟诚实则吾道明。夷狄禽兽无由而至。岂有今日之祸哉。是则讲学之会。不惟不可废。政宜百倍加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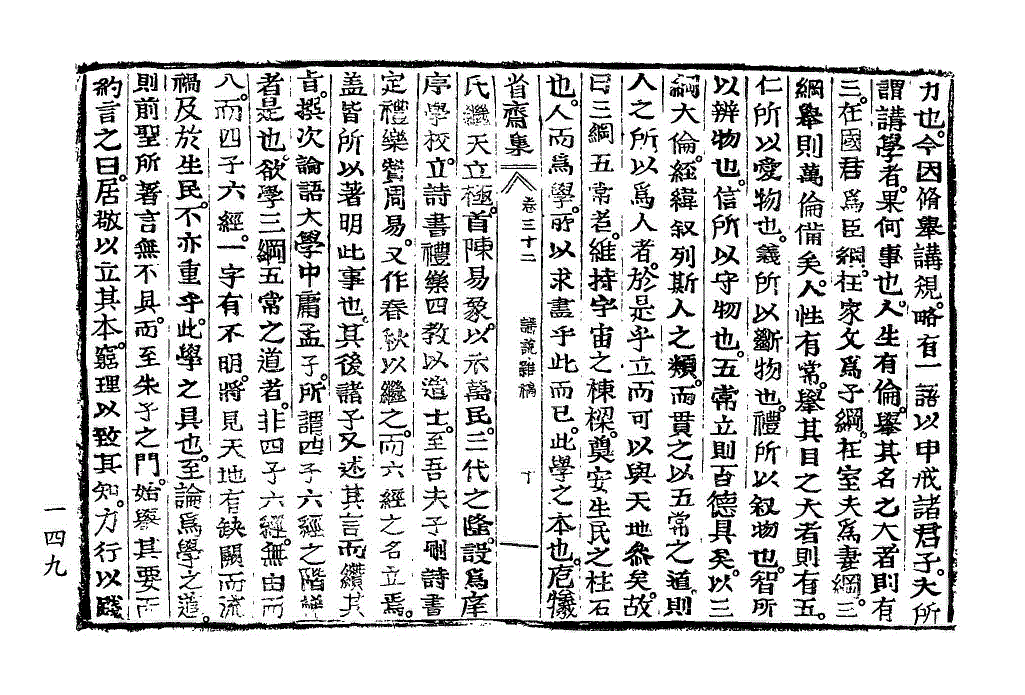 力也。今因脩举讲规。略有一语以申戒诸君子。夫所谓讲学者。果何事也。人生有伦。举其名之大者则有三。在国君为臣纲。在家父为子纲。在室夫为妻纲。三纲举则万伦备矣。人性有常。举其目之大者则有五。仁所以爱物也。义所以断物也。礼所以叙物也。智所以辨物也。信所以守物也。五常立则百德具矣。以三纲大伦。经纬叙列斯人之类。而贯之以五常之道。则人之所以为人者。于是乎立而可以与天地参矣。故曰三纲五常者。维持宇宙之栋梁。奠安生民之柱石也。人而为学。所以求尽乎此而已。此学之本也。庖牺氏继天立极。首陈易象。以示万民。三代之隆。设为庠序学校。立诗书礼乐四教以造士。至吾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又作春秋以继之。而六经之名立焉。盖皆所以著明此事也。其后诸子又述其言而缵其旨。撰次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者是也。欲学三纲五常之道者。非四子六经。无由而入。而四子六经。一字有不明。将见天地有缺阙而流祸及于生民。不亦重乎。此学之具也。至论为学之道。则前圣所著言无不具。而至朱子之门。始举其要而约言之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践
力也。今因脩举讲规。略有一语以申戒诸君子。夫所谓讲学者。果何事也。人生有伦。举其名之大者则有三。在国君为臣纲。在家父为子纲。在室夫为妻纲。三纲举则万伦备矣。人性有常。举其目之大者则有五。仁所以爱物也。义所以断物也。礼所以叙物也。智所以辨物也。信所以守物也。五常立则百德具矣。以三纲大伦。经纬叙列斯人之类。而贯之以五常之道。则人之所以为人者。于是乎立而可以与天地参矣。故曰三纲五常者。维持宇宙之栋梁。奠安生民之柱石也。人而为学。所以求尽乎此而已。此学之本也。庖牺氏继天立极。首陈易象。以示万民。三代之隆。设为庠序学校。立诗书礼乐四教以造士。至吾夫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又作春秋以继之。而六经之名立焉。盖皆所以著明此事也。其后诸子又述其言而缵其旨。撰次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者是也。欲学三纲五常之道者。非四子六经。无由而入。而四子六经。一字有不明。将见天地有缺阙而流祸及于生民。不亦重乎。此学之具也。至论为学之道。则前圣所著言无不具。而至朱子之门。始举其要而约言之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践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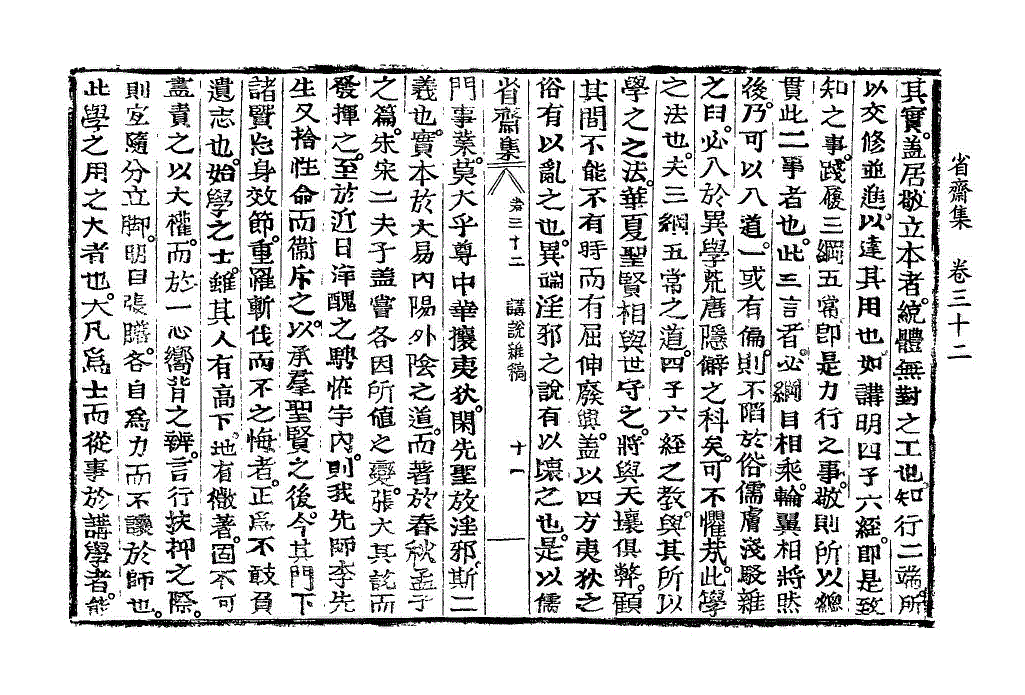 其实。盖居敬立本者。统体无对之工也。知行二端。所以交修并进。以达其用也。如讲明四子六经。即是致知之事。践履三纲五常。即是力行之事。敬则所以总贯此二事者也。此三言者。必纲目相乘。轮翼相将然后。乃可以入道。一或有偏。则不陷于俗儒肤浅驳杂之臼。必入于异学荒唐隐僻之科矣。可不惧哉。此学之法也。夫三纲五常之道。四子六经之教。与其所以学之之法。华夏圣贤相与世守之。将与天壤俱㢢。顾其间不能不有时而有屈伸废兴。盖以四方夷狄之俗有以乱之也。异端淫邪之说有以坏之也。是以儒门事业。莫大乎尊中华攘夷狄。闲先圣放淫邪。斯二义也。实本于大易内阳外阴之道。而著于春秋孟子之篇。朱宋二夫子盖尝各因所值之变。张大其说而发挥之。至于近日洋丑之骋怪宇内。则我先师李先生又舍性命而卫斥之。以承群圣贤之后。今其门下诸贤忘身效节。重罹斩伐而不之悔者。正为不敢负遗志也。始学之士。虽其人有高下。地有微著。固不可尽责之以大权。而于一心向背之辨。言行扶抑之际。则宜随分立脚。明目张胆。各自为力而不让于师也。此学之用之大者也。大凡为士而从事于讲学者。能
其实。盖居敬立本者。统体无对之工也。知行二端。所以交修并进。以达其用也。如讲明四子六经。即是致知之事。践履三纲五常。即是力行之事。敬则所以总贯此二事者也。此三言者。必纲目相乘。轮翼相将然后。乃可以入道。一或有偏。则不陷于俗儒肤浅驳杂之臼。必入于异学荒唐隐僻之科矣。可不惧哉。此学之法也。夫三纲五常之道。四子六经之教。与其所以学之之法。华夏圣贤相与世守之。将与天壤俱㢢。顾其间不能不有时而有屈伸废兴。盖以四方夷狄之俗有以乱之也。异端淫邪之说有以坏之也。是以儒门事业。莫大乎尊中华攘夷狄。闲先圣放淫邪。斯二义也。实本于大易内阳外阴之道。而著于春秋孟子之篇。朱宋二夫子盖尝各因所值之变。张大其说而发挥之。至于近日洋丑之骋怪宇内。则我先师李先生又舍性命而卫斥之。以承群圣贤之后。今其门下诸贤忘身效节。重罹斩伐而不之悔者。正为不敢负遗志也。始学之士。虽其人有高下。地有微著。固不可尽责之以大权。而于一心向背之辨。言行扶抑之际。则宜随分立脚。明目张胆。各自为力而不让于师也。此学之用之大者也。大凡为士而从事于讲学者。能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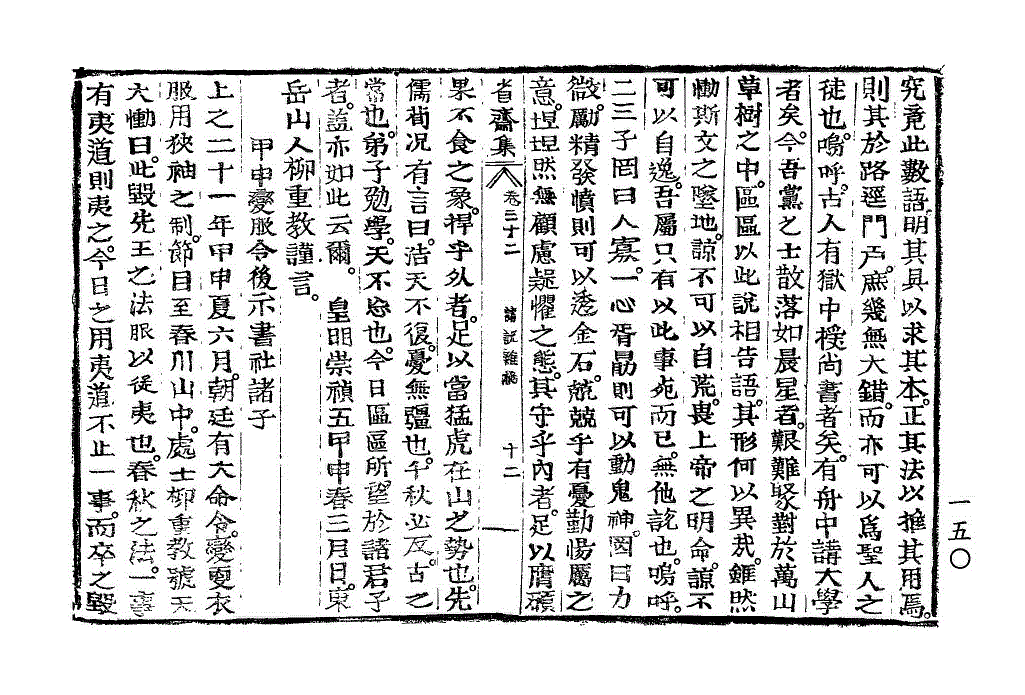 究竟此数语。明其具以求其本。正其法以推其用焉。则其于路径门户。庶几无大错。而亦可以为圣人之徒也。呜呼。古人有狱中授尚书者矣。有舟中讲大学者矣。今吾党之士散落如晨星者。艰难聚对于万山草树之中。区区以此说相告语。其形何以异哉。虽然恸斯文之坠地。谅不可以自荒。畏上帝之明命。谅不可以自逸。吾属只有以此事死而已。无他说也。呜呼。二三子罔曰人寡。一心胥勖则可以动鬼神。罔曰力微。励精发愤则可以透金石。兢兢乎有忧勤惕厉之意。坦坦然无顾虑疑惧之态。其守乎内者。足以膺硕果不食之象。捍乎外者。足以当猛虎在山之势也。先儒荀况有言曰。浩天不复。忧无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今日区区所望于诸君子者。盖亦如此云尔。 皇明崇祯五甲申春三月日。东岳山人柳重教谨言。
究竟此数语。明其具以求其本。正其法以推其用焉。则其于路径门户。庶几无大错。而亦可以为圣人之徒也。呜呼。古人有狱中授尚书者矣。有舟中讲大学者矣。今吾党之士散落如晨星者。艰难聚对于万山草树之中。区区以此说相告语。其形何以异哉。虽然恸斯文之坠地。谅不可以自荒。畏上帝之明命。谅不可以自逸。吾属只有以此事死而已。无他说也。呜呼。二三子罔曰人寡。一心胥勖则可以动鬼神。罔曰力微。励精发愤则可以透金石。兢兢乎有忧勤惕厉之意。坦坦然无顾虑疑惧之态。其守乎内者。足以膺硕果不食之象。捍乎外者。足以当猛虎在山之势也。先儒荀况有言曰。浩天不复。忧无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今日区区所望于诸君子者。盖亦如此云尔。 皇明崇祯五甲申春三月日。东岳山人柳重教谨言。甲申变服令后示书社诸子
上之二十一年甲申夏六月。朝廷有大命令。变更衣服用狭袖之制。节目至春川山中。处士柳重教号天大恸曰。此毁先王之法服以从夷也。春秋之法。一事有夷道则夷之。今日之用夷道不止一事。而卒之毁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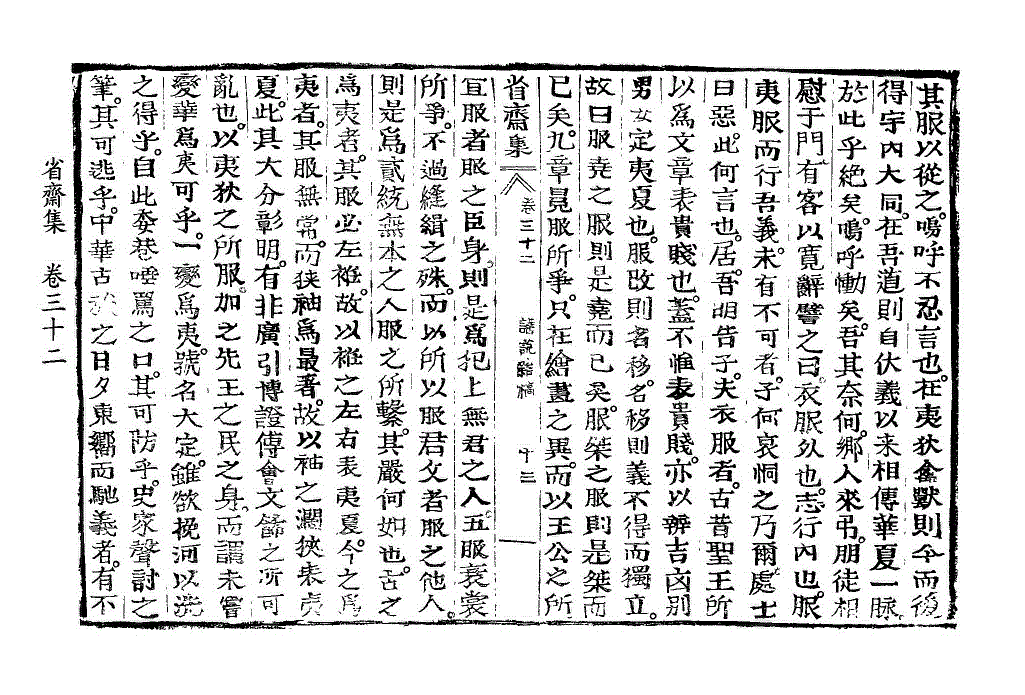 其服以从之。呜呼不忍言也。在夷狄禽兽则今而后得宇内大同。在吾道则自伏羲以来相传华夏一脉。于此乎绝矣。呜呼恸矣。吾其奈何。乡人来吊。朋徒相慰于门。有客以宽辞譬之曰。衣服外也。志行内也。服夷服而行吾义。未有不可者。子何哀恫之乃尔。处士曰恶。此何言也。居。吾明告子。夫衣服者。古昔圣王所以为文章表贵贱也。盖不惟表贵贱。亦以辨吉凶别男女定夷夏也。服改则名移。名移则义不得而独立。故曰服尧之服则是尧而已矣。服桀之服则是桀而已矣。九章冕服所争。只在绘画之异。而以王公之所宜服者服之臣身。则是为犯上无君之人。五服衰裳所争。不过缝缉之殊。而以所以服君父者服之他人。则是为贰统无本之人服之所系。其严何如也。古之为夷者。其服必左衽。故以衽之左右表夷夏。今之为夷者。其服无常。而狭袖为最著。故以袖之阔狭表夷夏。此其大分彰明。有非广引博證傅会文饰之所可乱也。以夷狄之所服。加之先王之民之身。而谓未尝变华为夷可乎。一变为夷。号名大定。虽欲挽河以洗之得乎。自此委巷唾骂之口。其可防乎。史家声讨之笔。其可逃乎。中华古族之日夕东向而驰义者。有不
其服以从之。呜呼不忍言也。在夷狄禽兽则今而后得宇内大同。在吾道则自伏羲以来相传华夏一脉。于此乎绝矣。呜呼恸矣。吾其奈何。乡人来吊。朋徒相慰于门。有客以宽辞譬之曰。衣服外也。志行内也。服夷服而行吾义。未有不可者。子何哀恫之乃尔。处士曰恶。此何言也。居。吾明告子。夫衣服者。古昔圣王所以为文章表贵贱也。盖不惟表贵贱。亦以辨吉凶别男女定夷夏也。服改则名移。名移则义不得而独立。故曰服尧之服则是尧而已矣。服桀之服则是桀而已矣。九章冕服所争。只在绘画之异。而以王公之所宜服者服之臣身。则是为犯上无君之人。五服衰裳所争。不过缝缉之殊。而以所以服君父者服之他人。则是为贰统无本之人服之所系。其严何如也。古之为夷者。其服必左衽。故以衽之左右表夷夏。今之为夷者。其服无常。而狭袖为最著。故以袖之阔狭表夷夏。此其大分彰明。有非广引博證傅会文饰之所可乱也。以夷狄之所服。加之先王之民之身。而谓未尝变华为夷可乎。一变为夷。号名大定。虽欲挽河以洗之得乎。自此委巷唾骂之口。其可防乎。史家声讨之笔。其可逃乎。中华古族之日夕东向而驰义者。有不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1L 页
 失声恸哭掖腕奋臂者乎。祖宗在天之灵。岂不赫然震怒乎。天地岂不丧其气。而日月岂不失其光乎。上而得罪于天地神明如此。下而失望于天下后世如此。而谓可以行吾义。吾谁欺。欺天乎。客曰子之言。处士之私议也。以君命之重压之。孰敢不从也。处士曰不然。君令而臣从。道其常耳。义之所不可。君命有所不受。亦处变之一大权也。天生烝民。莫不有其职。为大君者。奉天命布天职于庶官。庶官一受其命。则只知天职之为重。而不复苟徇其君之私情。故执法之官。执天子之父。而天子不得而禁之。持戟之士。闻将军之令。而不闻天子之诏。秉史笔之臣。伸百世之公议。而不掩君父之恶。夫所谓士者虽未尝有所受于公朝。而其所履亦天位也。其所修即天职也。盖任纲常之大柄。守圣贤之门庭。一代风气之所由定。万世议论之所由行。其职不亦重乎。国君有谬政关系名义之大防。而大臣不能止。谏官不能正。则士得以从违见情于下。以正一世之眼目。苟其志之不得遂焉。则又以身殉之。以伸大义于天下后世。虽以万乘之尊。其身可戮。其志不可夺也。何哉。天职为重而君命为轻也。且以尊君言之。前王后王。皆吾君也。畔弃前
失声恸哭掖腕奋臂者乎。祖宗在天之灵。岂不赫然震怒乎。天地岂不丧其气。而日月岂不失其光乎。上而得罪于天地神明如此。下而失望于天下后世如此。而谓可以行吾义。吾谁欺。欺天乎。客曰子之言。处士之私议也。以君命之重压之。孰敢不从也。处士曰不然。君令而臣从。道其常耳。义之所不可。君命有所不受。亦处变之一大权也。天生烝民。莫不有其职。为大君者。奉天命布天职于庶官。庶官一受其命。则只知天职之为重。而不复苟徇其君之私情。故执法之官。执天子之父。而天子不得而禁之。持戟之士。闻将军之令。而不闻天子之诏。秉史笔之臣。伸百世之公议。而不掩君父之恶。夫所谓士者虽未尝有所受于公朝。而其所履亦天位也。其所修即天职也。盖任纲常之大柄。守圣贤之门庭。一代风气之所由定。万世议论之所由行。其职不亦重乎。国君有谬政关系名义之大防。而大臣不能止。谏官不能正。则士得以从违见情于下。以正一世之眼目。苟其志之不得遂焉。则又以身殉之。以伸大义于天下后世。虽以万乘之尊。其身可戮。其志不可夺也。何哉。天职为重而君命为轻也。且以尊君言之。前王后王。皆吾君也。畔弃前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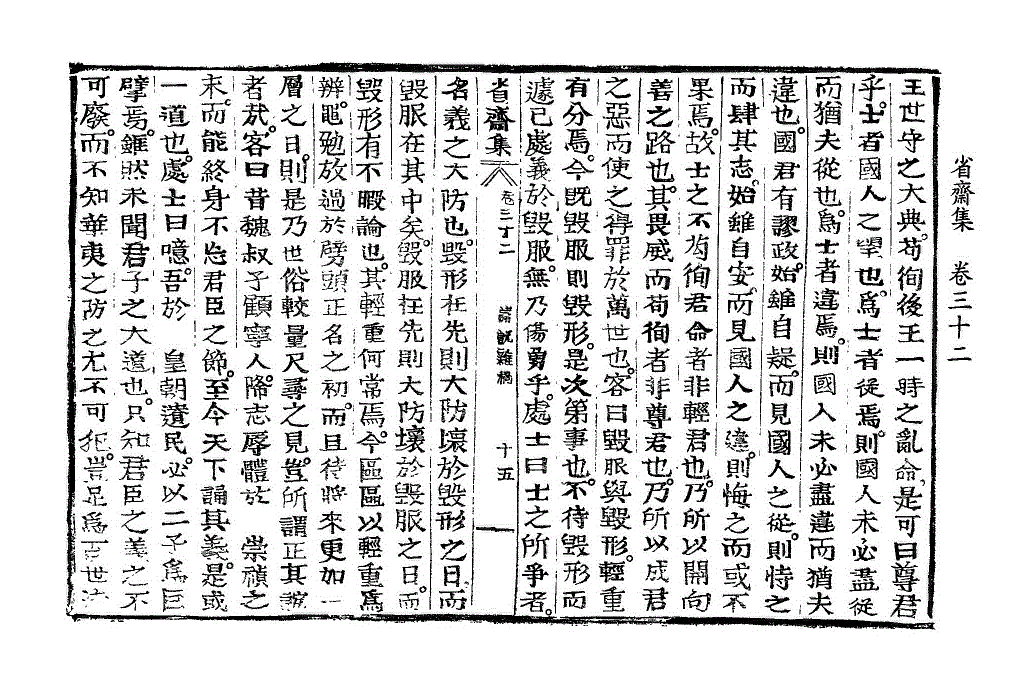 王世守之大典。苟徇后王一时之乱命。是可曰尊君乎。士者国人之望也。为士者从焉。则国人未必尽从而犹夫从也。为士者违焉。则国人未必尽违而犹夫违也。国君有谬政。始虽自疑。而见国人之从。则恃之而肆其志。始虽自安。而见国人之违。则悔之而或不果焉。故士之不苟徇君命者非轻君也。乃所以开向善之路也。其畏威而苟徇者非尊君也。乃所以成君之恶而使之得罪于万世也。客曰毁服与毁形。轻重有分焉。今既毁服则毁形。是次第事也。不待毁形而遽已处义于毁服。无乃伤勇乎。处士曰士之所争者。名义之大防也。毁形在先则大防坏于毁形之日。而毁服在其中矣。毁服在先则大防坏于毁服之日。而毁形有不暇论也。其轻重何常焉。今区区以轻重为辨。黾勉放过于劈头正名之初。而且待将来更加一层之日。则是乃世俗较量尺寻之见。岂所谓正其谊者哉。客曰昔魏叔子顾宁人。降志辱体于 崇祯之末。而能终身不忘君臣之节。至今天下诵其义。是或一道也。处士曰噫。吾于 皇朝遗民。必以二子为巨擘焉。虽然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只知君臣之义之不可废。而不知华夷之防之尤不可犯。岂足为百世法
王世守之大典。苟徇后王一时之乱命。是可曰尊君乎。士者国人之望也。为士者从焉。则国人未必尽从而犹夫从也。为士者违焉。则国人未必尽违而犹夫违也。国君有谬政。始虽自疑。而见国人之从。则恃之而肆其志。始虽自安。而见国人之违。则悔之而或不果焉。故士之不苟徇君命者非轻君也。乃所以开向善之路也。其畏威而苟徇者非尊君也。乃所以成君之恶而使之得罪于万世也。客曰毁服与毁形。轻重有分焉。今既毁服则毁形。是次第事也。不待毁形而遽已处义于毁服。无乃伤勇乎。处士曰士之所争者。名义之大防也。毁形在先则大防坏于毁形之日。而毁服在其中矣。毁服在先则大防坏于毁服之日。而毁形有不暇论也。其轻重何常焉。今区区以轻重为辨。黾勉放过于劈头正名之初。而且待将来更加一层之日。则是乃世俗较量尺寻之见。岂所谓正其谊者哉。客曰昔魏叔子顾宁人。降志辱体于 崇祯之末。而能终身不忘君臣之节。至今天下诵其义。是或一道也。处士曰噫。吾于 皇朝遗民。必以二子为巨擘焉。虽然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只知君臣之义之不可废。而不知华夷之防之尤不可犯。岂足为百世法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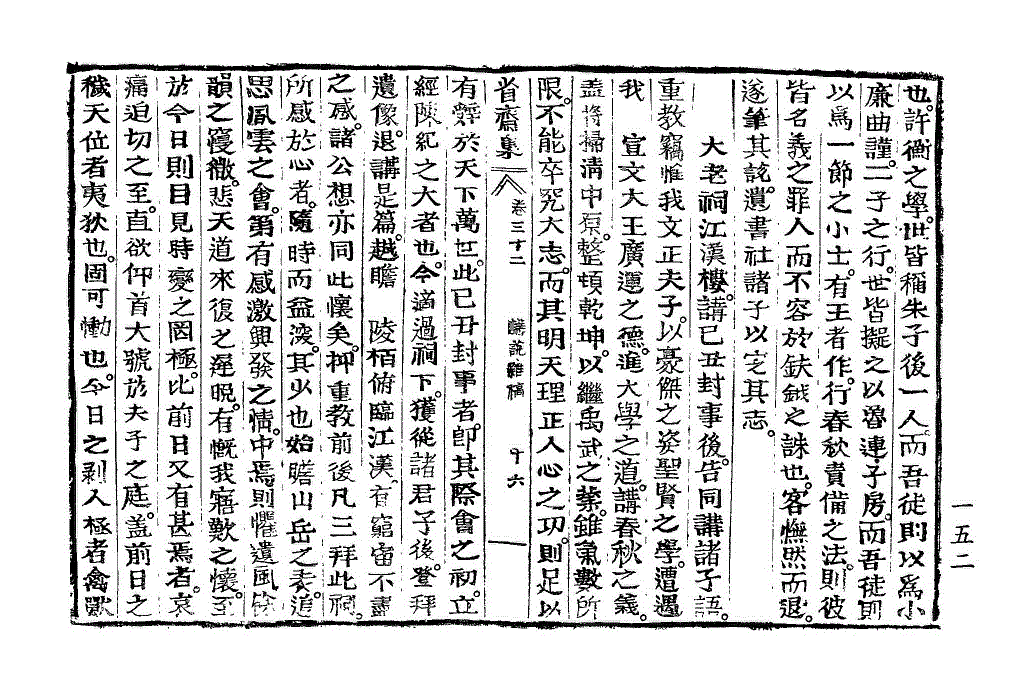 也。许衡之学。世皆称朱子后一人。而吾徒则以为小廉曲谨。二子之行。世皆拟之以鲁连,子房。而吾徒则以为一节之小士。有王者作。行春秋责备之法。则彼皆名义之罪人而不容于鈇钺之诛也。客怃然而退。遂笔其说。遗书社诸子以定其志。
也。许衡之学。世皆称朱子后一人。而吾徒则以为小廉曲谨。二子之行。世皆拟之以鲁连,子房。而吾徒则以为一节之小士。有王者作。行春秋责备之法。则彼皆名义之罪人而不容于鈇钺之诛也。客怃然而退。遂笔其说。遗书社诸子以定其志。大老祠江汉楼。讲己丑封事后。告同讲诸子语。
重教窃惟我文正夫子。以豪杰之姿圣贤之学。遭遇我 宣文大王广运之德。进大学之道。讲春秋之义。盖将扫清中原。整顿乾坤。以继禹武之业。虽气数所限。不能卒究大志。而其明天理正人心之功。则足以有辞于天下万世。此己丑封事者。即其际会之初。立经陈纪之大者也。今适过祠下。获从诸君子后。登拜遗像。退讲是篇。越瞻 陵柏俯临江汉。有穷宙不尽之感。诸公想亦同此怀矣。抑重教前后凡三拜此祠。所感于心者。随时而益深。其少也始瞻山岳之表。追思风云之会。第有感激兴发之情。中焉则惧遗风馀韵之寝微。悲天道来复之迟晚。有慨我寤叹之怀。至于今日则目见时变之罔极。比前日又有甚焉者。哀痛迫切之至。直欲仰首大号于夫子之庭。盖前日之秽天位者夷狄也。固可恸也。今日之剥人极者禽兽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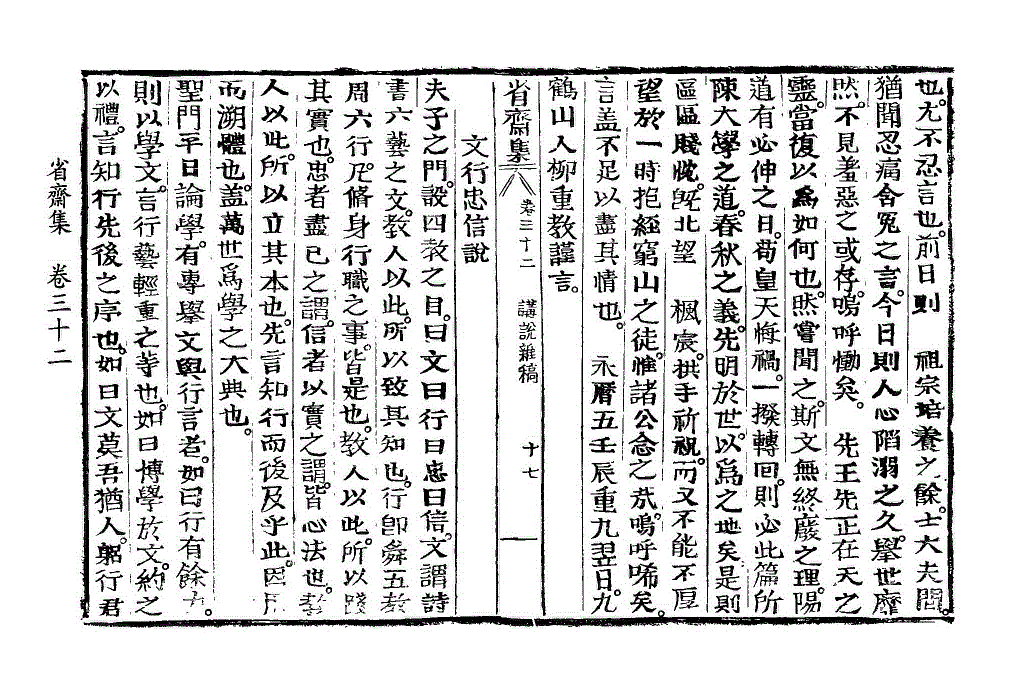 也。尤不忍言也。前日则 祖宗培养之馀。士大夫间。犹闻忍痛含冤之言。今日则人心陷溺之久。举世靡然。不见羞恶之或存。呜呼恸矣。 先王先正在天之灵。当复以为如何也。然尝闻之。斯文无终废之理。阳道有必伸之日。苟皇天悔祸。一拨转回。则必此篇所陈大学之道。春秋之义。先明于世。以为之地矣。是则区区贱忱。既北望 枫宸。拱手祈祝。而又不能不厚望于一时抱经穷山之徒。惟诸公念之哉。呜呼唏矣。言盖不足以尽其情也。 永历五壬辰重九翌日。九鹤山人柳重教谨言。
也。尤不忍言也。前日则 祖宗培养之馀。士大夫间。犹闻忍痛含冤之言。今日则人心陷溺之久。举世靡然。不见羞恶之或存。呜呼恸矣。 先王先正在天之灵。当复以为如何也。然尝闻之。斯文无终废之理。阳道有必伸之日。苟皇天悔祸。一拨转回。则必此篇所陈大学之道。春秋之义。先明于世。以为之地矣。是则区区贱忱。既北望 枫宸。拱手祈祝。而又不能不厚望于一时抱经穷山之徒。惟诸公念之哉。呜呼唏矣。言盖不足以尽其情也。 永历五壬辰重九翌日。九鹤山人柳重教谨言。文行忠信说
夫子之门。设四教之目。曰文曰行曰忠曰信。文谓诗书六艺之文。教人以此。所以致其知也。行即舜五教周六行。凡脩身行职之事。皆是也。教人以此。所以践其实也。忠者尽己之谓。信者以实之谓。皆心法也。教人以此。所以立其本也。先言知行而后及乎此。因用而溯体也。盖万世为学之大典也。
圣门平日论学。有专举文与行言者。如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言行艺轻重之等也。如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言知行先后之序也。如曰文莫吾犹人。躬行君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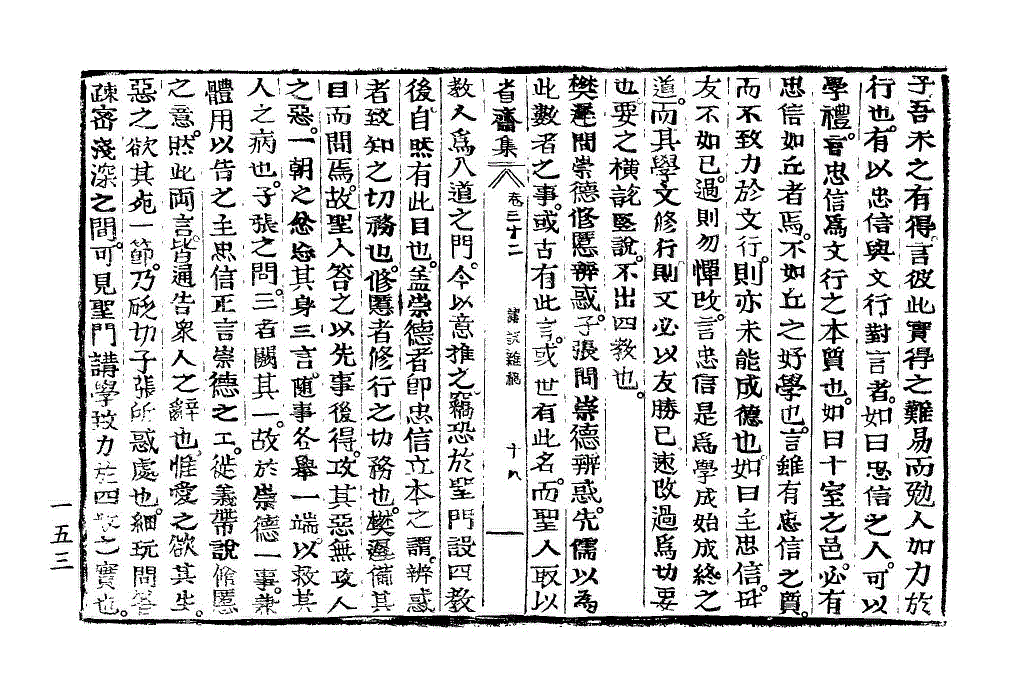 子。吾未之有得。言彼此实得之难易而勉人加力于行也。有以忠信与文行对言者。如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忠信为文行之本质也。如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言虽有忠信之质。而不致力于文行。则亦未能成德也。如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过则勿惮改。言忠信是为学成始成终之道。而其学文修行。则又必以友胜己。速改过为切要也。要之横说竖说。不出四教也。
子。吾未之有得。言彼此实得之难易而勉人加力于行也。有以忠信与文行对言者。如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忠信为文行之本质也。如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言虽有忠信之质。而不致力于文行。则亦未能成德也。如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过则勿惮改。言忠信是为学成始成终之道。而其学文修行。则又必以友胜己。速改过为切要也。要之横说竖说。不出四教也。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子张问崇德辨惑。先儒以为此数者之事。或古有此言。或世有此名。而圣人取以教人为入道之门。今以意推之。窃恐于圣门设四教后。自然有此目也。盖崇德者即忠信立本之谓。辨惑者致知之切务也。修慝者修行之切务也。樊迟备其目而问焉。故圣人答之以先事后得。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一朝之忿忘其身三言。随事各举一端。以救其人之病也。子张之问。三者阙其一。故于崇德一事。兼体用以告之主忠信正言崇德之工。徙义带说脩慝之意。然此两言。皆通告众人之辞也。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一节。乃砭切子张所惑处也。细玩问答疏密浅深之间。可见圣门讲学致力于四教之实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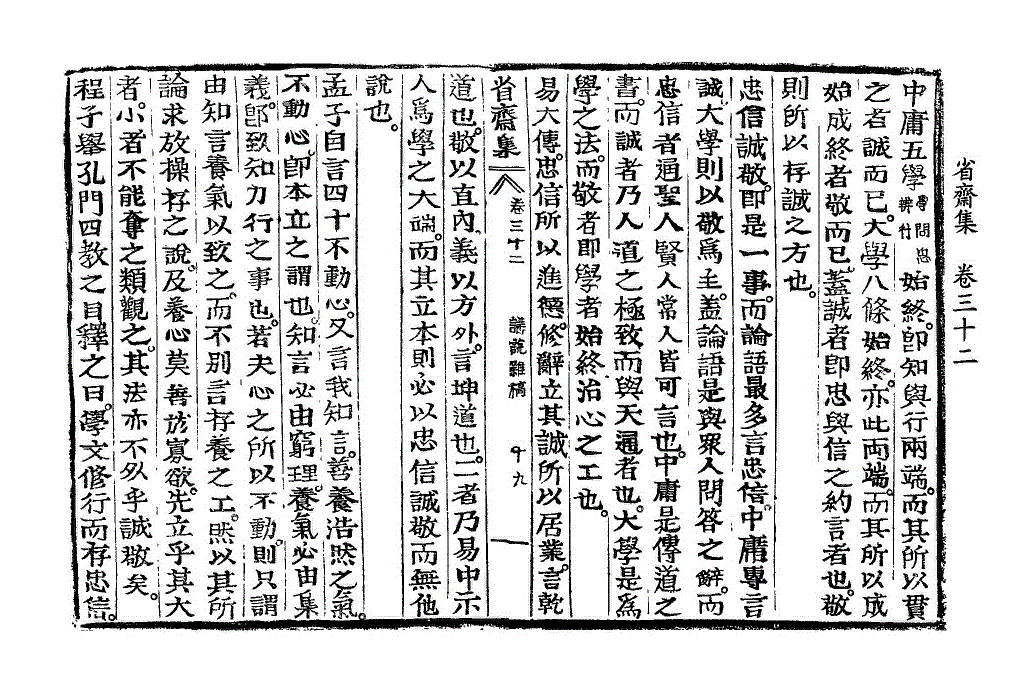 中庸五学(学问思辨行)始终。即知与行两端。而其所以贯之者诚而已。大学八条始终。亦此两端。而其所以成始成终者敬而已。盖诚者即忠与信之约言者也。敬则所以存诚之方也。
中庸五学(学问思辨行)始终。即知与行两端。而其所以贯之者诚而已。大学八条始终。亦此两端。而其所以成始成终者敬而已。盖诚者即忠与信之约言者也。敬则所以存诚之方也。忠信诚敬。即是一事。而论语最多言忠信。中庸专言诚。大学则以敬为主。盖论语是与众人问答之辞。而忠信者通圣人贤人常人皆可言也。中庸是传道之书。而诚者乃人道之极致而与天通者也。大学是为学之法。而敬者即学者始终治心之工也。
易大传。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言乾道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言坤道也。二者乃易中示人为学之大端。而其立本则必以忠信诚敬而无他说也。
孟子自言四十不动心。又言我知言。善养浩然之气。不动心。即本立之谓也。知言必由穷理。养气必由集义。即致知力行之事也。若夫心之所以不动。则只谓由知言养气以致之。而不别言存养之工。然以其所论求放操存之说。及养心莫善于寡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夺之类观之。其法亦不外乎诚敬矣。
程子举孔门四教之目释之曰。学文修行而存忠信。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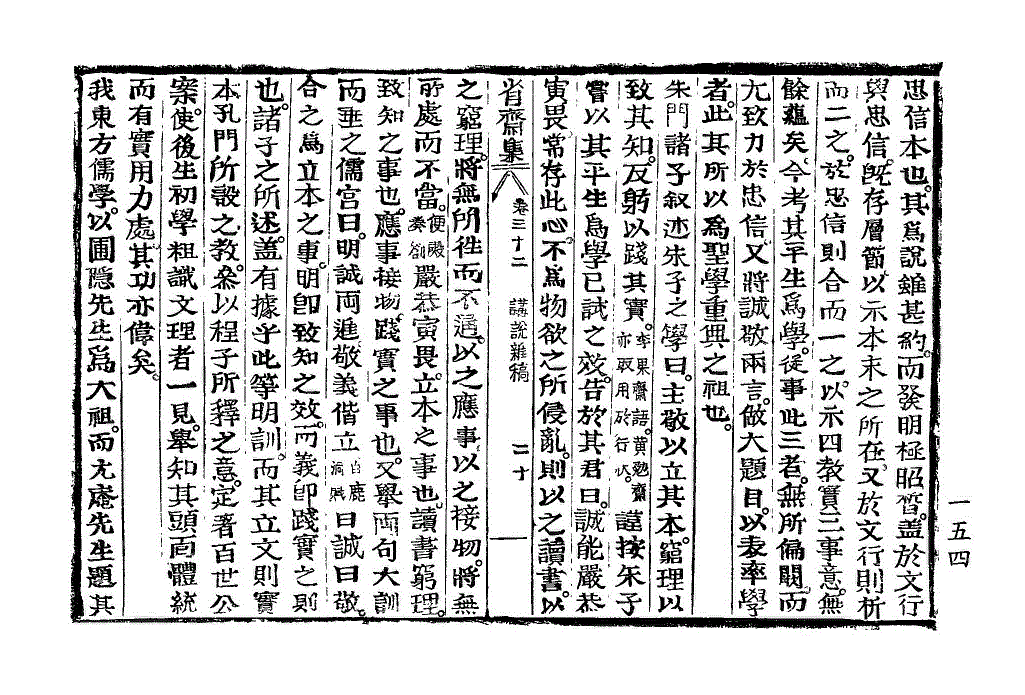 忠信本也。其为说虽甚约。而发明极昭晰。盖于文行与忠信。既存层节。以示本末之所在。又于文行则析而二之。于忠信则合而一之。以示四教实三事意。无馀蕴矣。今考其平生为学。从事此三者。无所偏阙。而尤致力于忠信。又将诚敬两言。做大题目。以表率学者。此其所以为圣学重兴之祖也。
忠信本也。其为说虽甚约。而发明极昭晰。盖于文行与忠信。既存层节。以示本末之所在。又于文行则析而二之。于忠信则合而一之。以示四教实三事意。无馀蕴矣。今考其平生为学。从事此三者。无所偏阙。而尤致力于忠信。又将诚敬两言。做大题目。以表率学者。此其所以为圣学重兴之祖也。朱门诸子叙述朱子之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李果斋语。黄勉斋亦取用于行状。)谨按朱子尝以其平生为学已试之效。告于其君曰。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穷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便殿奏劄)严恭寅畏。立本之事也。读书穷理。致知之事也。应事接物。践实之事也。又举两句大训而垂之儒宫曰。明诚两进。敬义偕立(白鹿洞赋)曰诚曰敬。合之为立本之事。明即致知之效。而义即践实之则也。诸子之所述。盖有据乎此等明训。而其立文则实本孔门所设之教。参以程子所释之意。定著百世公案。使后生初学粗识文理者一见。举知其头面体统而有实用力处。其功亦伟矣。
我东方儒学。以圃隐先生为大祖。而尤庵先生题其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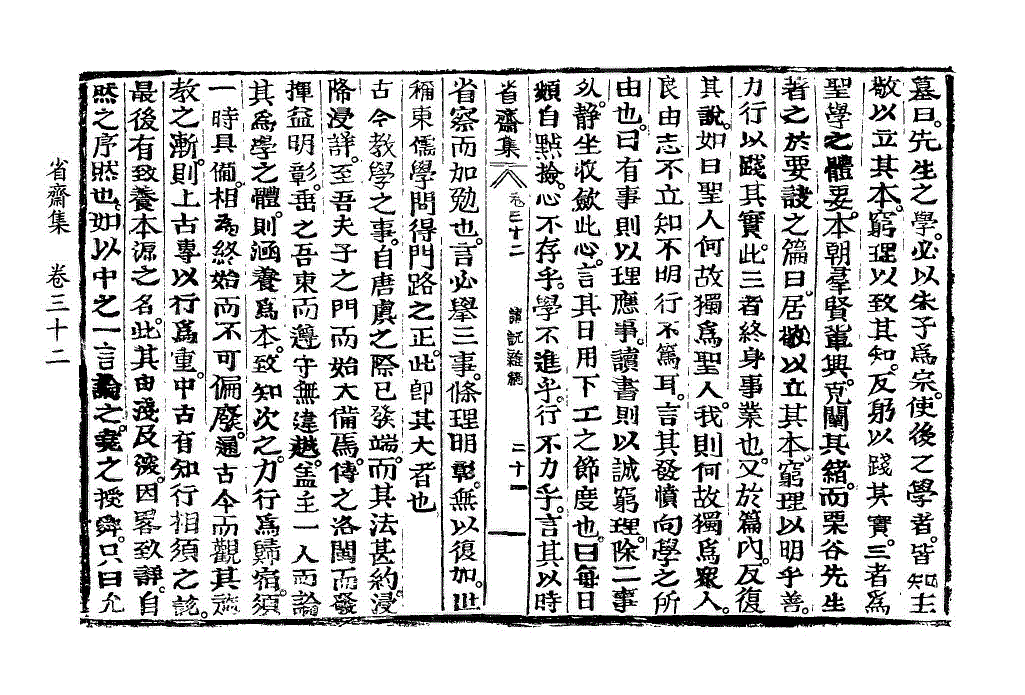 墓曰。先生之学。必以朱子为宗。使后之学者。皆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三者为圣学之体要。本朝群贤辈兴。克阐其绪。而栗谷先生著之于要诀之篇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明乎善。力行以践其实。此三者终身事业也。又于篇内。反复其说。如曰圣人何故独为圣人。我则何故独为众人。良由志不立知不明行不笃耳。言其发愤向学之所由也。曰有事则以理应事。读书则以诚穷理。除二事外。静坐收敛此心。言其日用下工之节度也。曰每日频自点捡。心不存乎。学不进乎。行不力乎。言其以时省察而加勉也。言必举三事。条理明彰。无以复加。世称东儒学问得门路之正。此即其大者也。
墓曰。先生之学。必以朱子为宗。使后之学者。皆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三者为圣学之体要。本朝群贤辈兴。克阐其绪。而栗谷先生著之于要诀之篇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明乎善。力行以践其实。此三者终身事业也。又于篇内。反复其说。如曰圣人何故独为圣人。我则何故独为众人。良由志不立知不明行不笃耳。言其发愤向学之所由也。曰有事则以理应事。读书则以诚穷理。除二事外。静坐收敛此心。言其日用下工之节度也。曰每日频自点捡。心不存乎。学不进乎。行不力乎。言其以时省察而加勉也。言必举三事。条理明彰。无以复加。世称东儒学问得门路之正。此即其大者也。古今教学之事。自唐虞之际已发端。而其法甚约。浸降浸详。至吾夫子之门而始大备焉。传之洛闽而发挥益明彰。垂之吾东而遵守无违越。盖主一人而论其为学之体。则涵养为本。致知次之。力行为归宿。须一时具备。相为终始而不可偏废。通古今而观其施教之渐。则上古专以行为重。中古有知行相须之说。最后有致养本源之名。此其由浅及深。因略致详。自然之序然也。如以中之一言论之。尧之授舜。只曰允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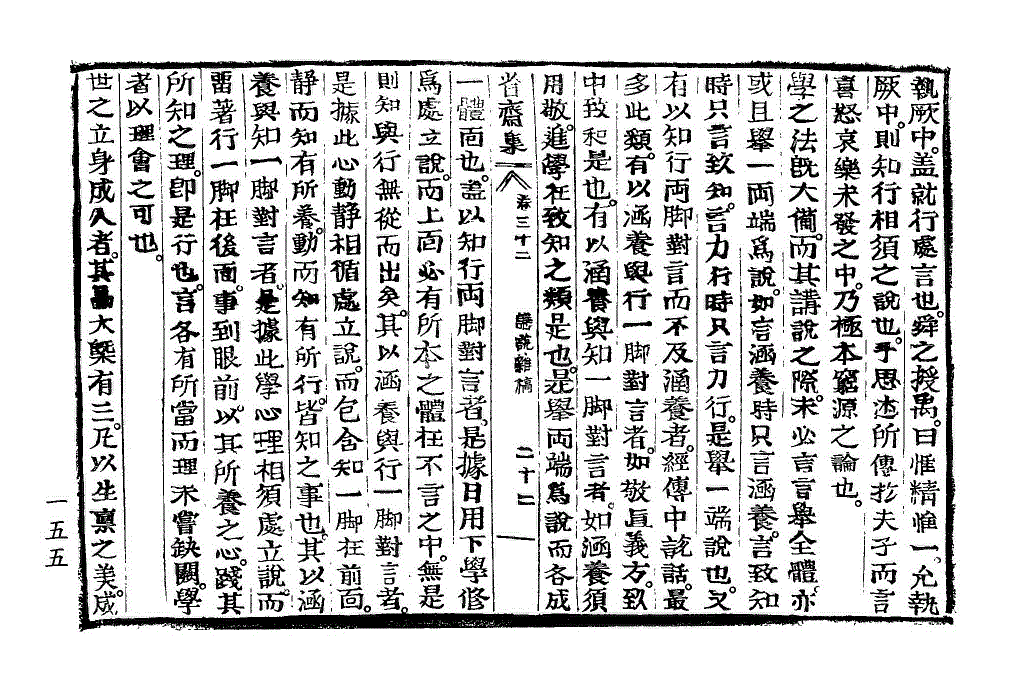 执厥中。盖就行处言也。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知行相须之说也。子思述所传于夫子而言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乃极本穷源之论也。
执厥中。盖就行处言也。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知行相须之说也。子思述所传于夫子而言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乃极本穷源之论也。学之法既大备。而其讲说之际。未必言言举全体。亦或且举一两端为说。如言涵养时只言涵养。言致知时只言致知。言力行时只言力行。是举一端说也。又有以知行两脚对言而不及涵养者。经传中说话。最多此类。有以涵养与行一脚对言者。如敬直义方。致中致和是也。有以涵养与知一脚对言者。如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类是也。是举两端为说而各成一体面也。盖以知行两脚对言者。是据日用下学修为处立说。而上面必有所本之体在不言之中。无是则知与行无从而出矣。其以涵养与行一脚对言者。是据此心动静相循处立说。而包含知一脚在前面。静而知有所养。动而知有所行。皆知之事也。其以涵养与知一脚对言者。是据此学心理相须处立说。而留著行一脚在后面。事到眼前。以其所养之心。践其所知之理。即是行也。言各有所当而理未尝缺阙。学者以理会之可也。
世之立身成人者。其品大槩有三。凡以生禀之美。成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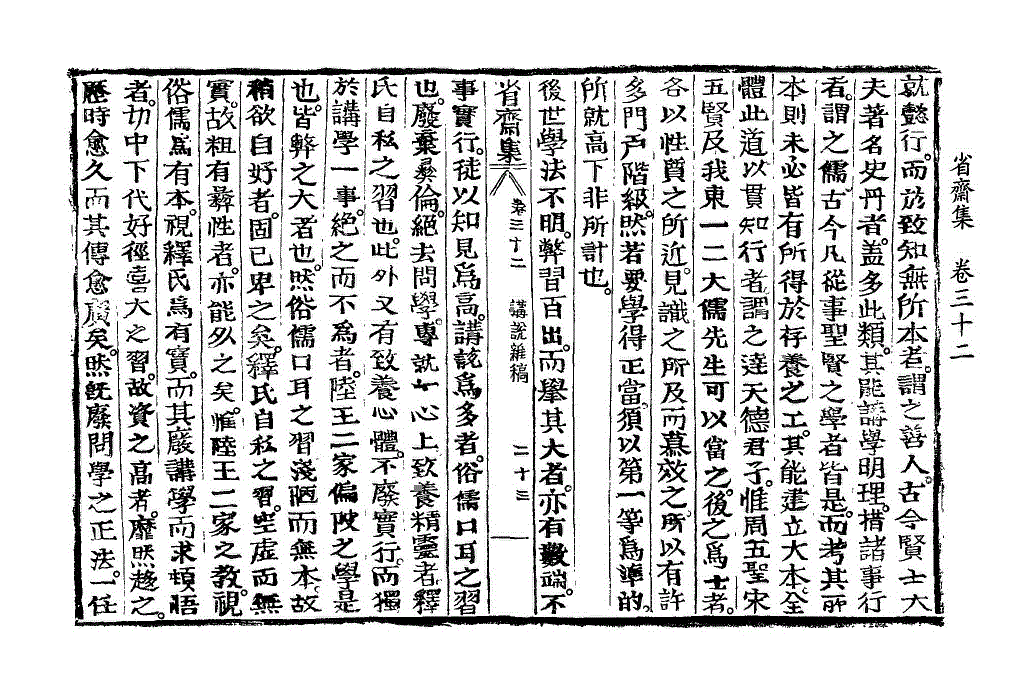 就懿行。而于致知无所本者。谓之善人。古今贤士大夫著名史册者。盖多此类。其能讲学明理。措诸事行者。谓之儒。古今凡从事圣贤之学者皆是。而考其所本则未必皆有所得于存养之工。其能建立大本。全体此道以贯知行者。谓之达天德君子。惟周五圣宋五贤及我东一二大儒先生可以当之。后之为士者。各以性质之所近。见识之所及而慕效之。所以有许多门户阶级。然若要学得正当。须以第一等为准的。所就高下非所计也。
就懿行。而于致知无所本者。谓之善人。古今贤士大夫著名史册者。盖多此类。其能讲学明理。措诸事行者。谓之儒。古今凡从事圣贤之学者皆是。而考其所本则未必皆有所得于存养之工。其能建立大本。全体此道以贯知行者。谓之达天德君子。惟周五圣宋五贤及我东一二大儒先生可以当之。后之为士者。各以性质之所近。见识之所及而慕效之。所以有许多门户阶级。然若要学得正当。须以第一等为准的。所就高下非所计也。后世学法不明。㢢习百出。而举其大者。亦有数端。不事实行。徒以知见为高。讲说为多者。俗儒口耳之习也。废弃彝伦。绝去问学。专就一心上致养精灵者。释氏自私之习也。此外又有致养心体。不废实行。而独于讲学一事。绝之而不为者。陆王二家偏陂之学是也。皆㢢之大者也。然俗儒口耳之习浅陋而无本。故稍欲自好者。固已卑之矣。释氏自私之习。空虚而无实。故粗有彝性者。亦能外之矣。惟陆王二家之教。视俗儒为有本。视释氏为有实。而其废讲学而求顿悟者。切中下代好径喜大之习。故资之高者。靡然趍之。历时愈久而其传愈广矣。然既废问学之正法。一任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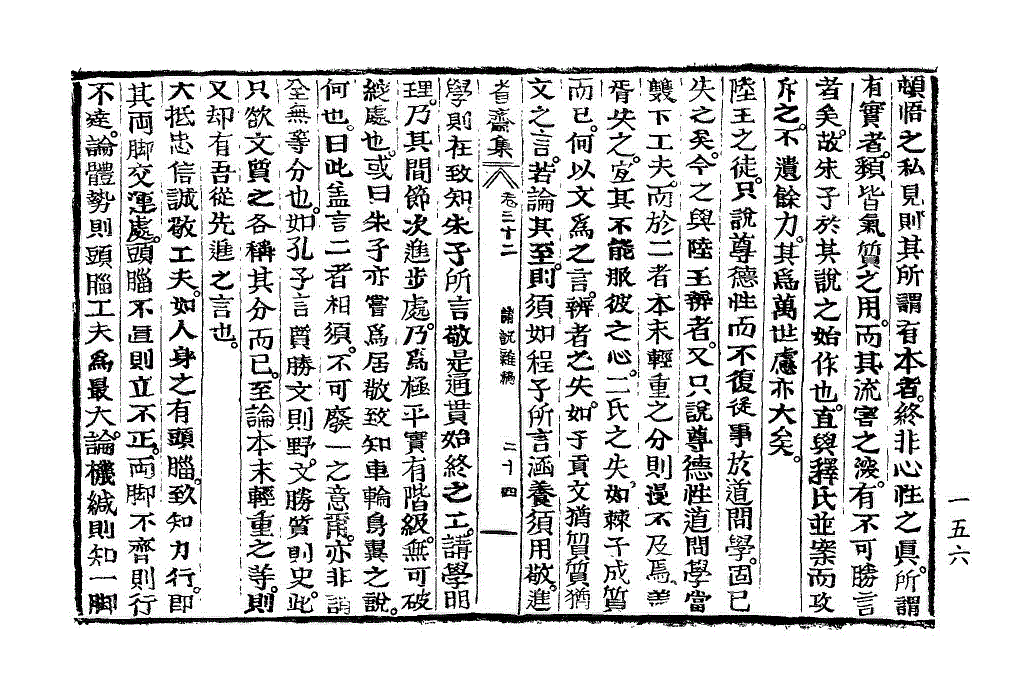 顿悟之私见。则其所谓有本者。终非心性之真。所谓有实者。类皆气质之用。而其流害之深。有不可胜言者矣。故朱子于其说之始作也。直与释氏并案而攻斥之。不遗馀力。其为万世虑亦大矣。
顿悟之私见。则其所谓有本者。终非心性之真。所谓有实者。类皆气质之用。而其流害之深。有不可胜言者矣。故朱子于其说之始作也。直与释氏并案而攻斥之。不遗馀力。其为万世虑亦大矣。陆王之徒。只说尊德性而不复从事于道问学。固已失之矣。今之与陆王辨者。又只说尊德性道问学当双下工夫。而于二者本末轻重之分则漫不及焉。盖胥失之。宜其不能服彼之心。二氏之失。如棘子成质而已。何以文为之言。辨者之失。如子贡文犹质质犹文之言。若论其至。则须如程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所言敬是通贯始终之工。讲学明理。乃其间节次进步处。乃为极平实有阶级。无可破绽处也。或曰朱子亦尝为居敬致知车轮鸟翼之说。何也。曰此盖言二者相须。不可废一之意尔。亦非谓全无等分也。如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只欲文质之各称其分而已。至论本末轻重之等。则又却有吾从先进之言也。
大抵忠信诚敬工夫。如人身之有头脑。致知力行。即其两脚交运处。头脑不直则立不正。两脚不齐则行不达。论体势则头脑工夫为最大。论机缄则知一脚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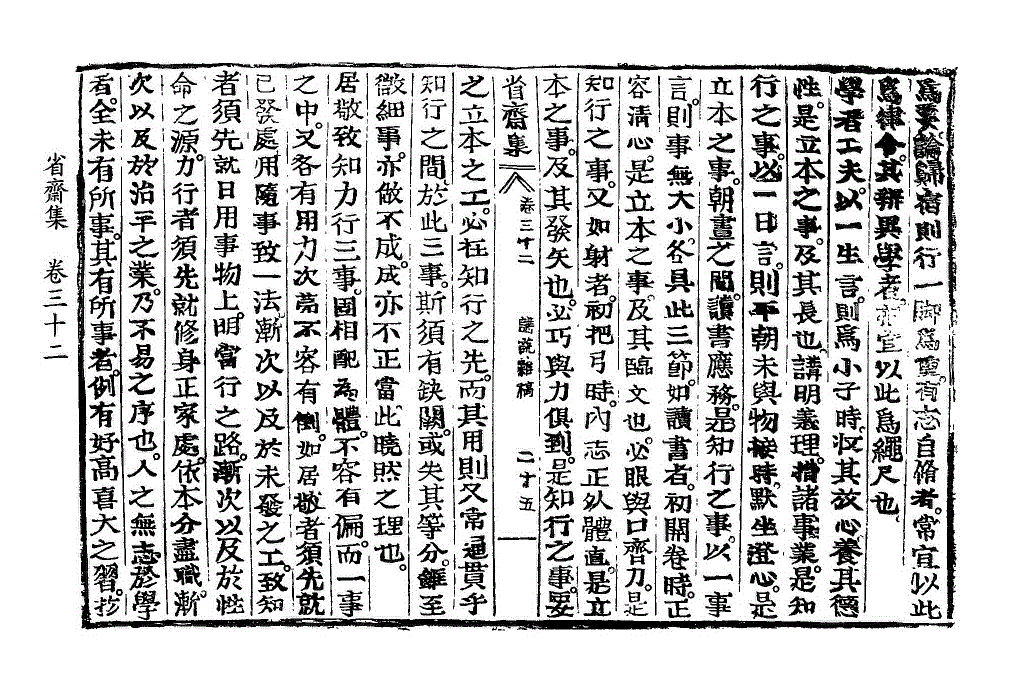 为要。论归宿则行一脚为重。有志自脩者。常宜以此为律令。其辨异学者。亦宜以此为绳尺也。
为要。论归宿则行一脚为重。有志自脩者。常宜以此为律令。其辨异学者。亦宜以此为绳尺也。学者工夫。以一生言。则为小子时。收其放心。养其德性。是立本之事。及其长也。讲明义理。措诸事业。是知行之事。以一日言。则平朝未与物接时。默坐澄心。是立本之事。朝昼之间。读书应务。是知行之事。以一事言。则事无大小。各具此三节。如读书者。初开卷时。正容清心。是立本之事。及其临文也。必眼与口齐力。是知行之事。又如射者。初把弓时。内志正外体直。是立本之事。及其发矢也。必巧与力俱到。是知行之事。要之立本之工。必在知行之先。而其用则又常通贯乎知行之间。于此三事。斯须有缺阙。或失其等分。虽至微细事。亦做不成。成亦不正当。此晓然之理也。
居敬致知力行三事。固相配为体。不容有偏。而一事之中。又各有用力次第不容有倒。如居敬者须先就已发处用随事致一法。渐次以及于未发之工。致知者须先就日用事物上。明当行之路。渐次以及于性命之源。力行者须先就修身正家处。依本分尽职。渐次以及于治平之业。乃不易之序也。人之无志于学者。全未有所事。其有所事者。例有好高喜大之习。于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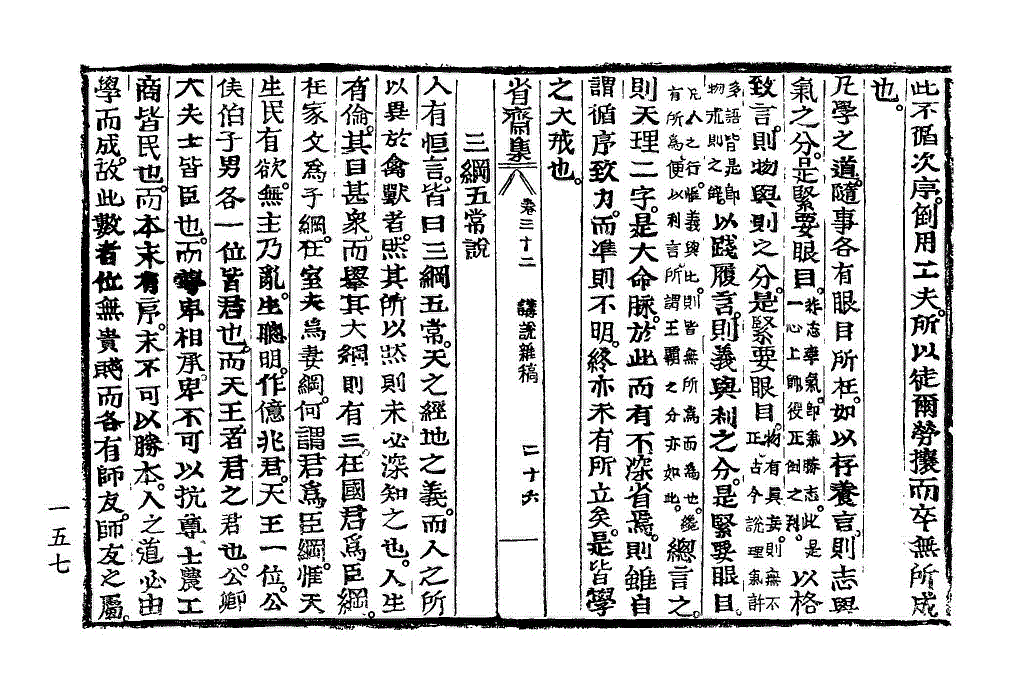 此不循次序。倒用工夫。所以徒尔劳攘而卒无所成也。
此不循次序。倒用工夫。所以徒尔劳攘而卒无所成也。凡学之道。随事各有眼目所在。如以存养言。则志与气之分。是紧要眼目。(非志率气。即气胜志。此是一心上师役正倒之判。)以格致言。则物与则之分。是紧要眼目。(物有真妄。则无不正。古今说理气许多语皆是即物求则之辞。)以践履言。则义与利之分。是紧要眼目。(凡人之行。惟义与比。则皆无所为而为也。才有所为。便以利言。所谓王霸之分亦如此。)总言之。则天理二字。是大命脉。于此而有不深省焉。则虽自谓循序致力。而准则不明。终亦未有所立矣。是皆学之大戒也。
三纲五常说
人有恒言。皆曰三纲五常。天之经地之义。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然其所以然则未必深知之也。人生有伦。其目甚众。而举其大纲则有三。在国君为臣纲。在家父为子纲。在室夫为妻纲。何谓君为臣纲。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生聪明。作亿兆君。天王一位。公侯伯子男各一位皆君也。而天王者君之君也。公卿大夫士皆臣也。而尊卑相承。卑不可以抗尊。士农工商皆民也。而本末有序。末不可以胜本。人之道必由学而成。故此数者位无贵贱而各有师友。师友之属。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8H 页
 以德为差。是皆公天下之大伦也。而语其至尊而无对则君而已。何谓父为子纲。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父道焉然后有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子之生有先后。斯有兄弟之序。兄弟非一人。斯有伯仲叔季之名。其所出有贵贱。斯有嫡庶之等。所继有轻重。斯有宗支之分。所分有远近。斯有亲戚宗族疏戚之差。是皆有家天属之大者也。而语其至尊而无对则父而已。何谓夫为妻纲。生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故必夫妇合体而后成造化。夫妇之伦。惟天子为备。天子后一夫人三。嫔九世妇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尊卑相承。若外朝之有公卿大夫士。诸侯夫人一媵二。三人各有娣侄二。凡六。大夫妻一。妾有贵妾有贱妾。士一妻一妾。庶人一妻而已。是皆男女居室之伦也。而语其至尊而无对则夫而已。此三者之于人伦。若网之有纲。一或有隳则万目从而沦焉。故皆得纲之名。人之有道。其端不一。而举其大经则有五。仁所以爱物也。义所以断物也。礼所以叙物也。智所以辨物也。信所以守物也。夫仁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故其性为仁。而其施于用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好生之德。如春嘘而物茁。
以德为差。是皆公天下之大伦也。而语其至尊而无对则君而已。何谓父为子纲。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父道焉然后有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子之生有先后。斯有兄弟之序。兄弟非一人。斯有伯仲叔季之名。其所出有贵贱。斯有嫡庶之等。所继有轻重。斯有宗支之分。所分有远近。斯有亲戚宗族疏戚之差。是皆有家天属之大者也。而语其至尊而无对则父而已。何谓夫为妻纲。生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故必夫妇合体而后成造化。夫妇之伦。惟天子为备。天子后一夫人三。嫔九世妇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尊卑相承。若外朝之有公卿大夫士。诸侯夫人一媵二。三人各有娣侄二。凡六。大夫妻一。妾有贵妾有贱妾。士一妻一妾。庶人一妻而已。是皆男女居室之伦也。而语其至尊而无对则夫而已。此三者之于人伦。若网之有纲。一或有隳则万目从而沦焉。故皆得纲之名。人之有道。其端不一。而举其大经则有五。仁所以爱物也。义所以断物也。礼所以叙物也。智所以辨物也。信所以守物也。夫仁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故其性为仁。而其施于用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好生之德。如春嘘而物茁。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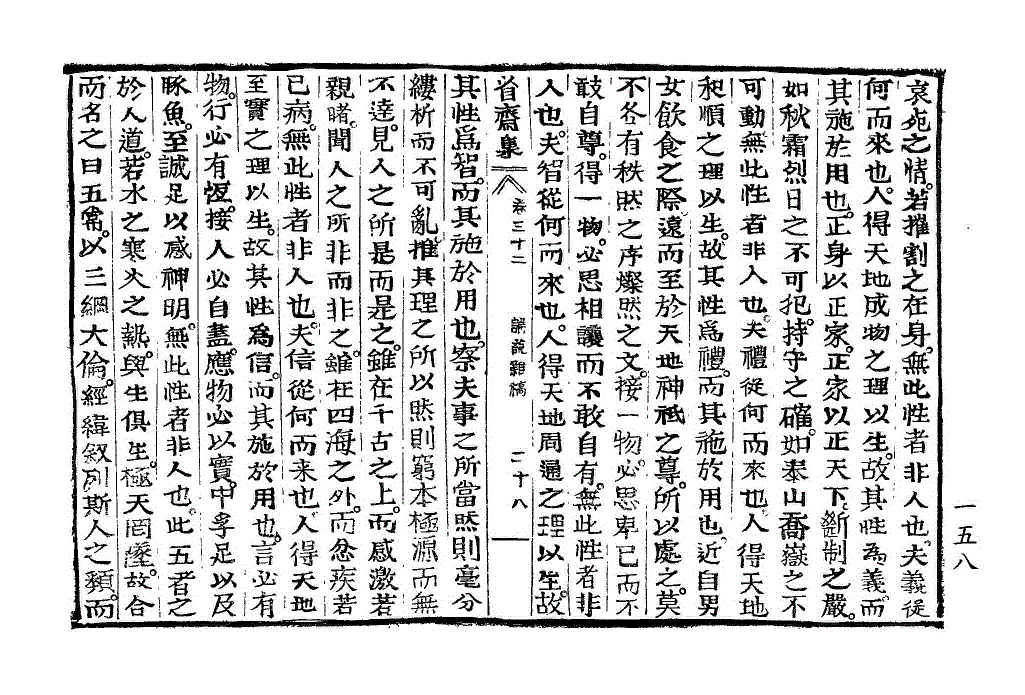 哀死之情。若摧割之在身。无此性者非人也。夫义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成物之理以生。故其性为义。而其施于用也。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断制之严。如秋霜烈日之不可犯。持守之确。如泰山乔岳之不可动。无此性者非人也。夫礼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和顺之理以生。故其性为礼。而其施于用也。近自男女饮食之际。远而至于天地神祗之尊。所以处之。莫不各有秩然之序灿然之文。接一物。必思卑已而不敢自尊。得一物。必思相让而不敢自有。无此性者非人也。夫智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周通之理以生。故其性为智。而其施于用也。察夫事之所当然则毫分缕析而不可乱。推其理之所以然则穷本极源而无不达。见人之所是而是之。虽在千古之上。而感激若亲睹。闻人之所非而非之。虽在四海之外。而忿疾若己病。无此性者非人也。夫信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至实之理以生。故其性为信。而其施于用也。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接人必自尽。应物必以实。中孚足以及豚鱼。至诚足以感神明。无此性者非人也。此五者之于人道。若水之寒火之热。与生俱生。极天罔坠。故合而名之曰五常。以三纲大伦。经纬叙列斯人之类。而
哀死之情。若摧割之在身。无此性者非人也。夫义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成物之理以生。故其性为义。而其施于用也。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断制之严。如秋霜烈日之不可犯。持守之确。如泰山乔岳之不可动。无此性者非人也。夫礼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和顺之理以生。故其性为礼。而其施于用也。近自男女饮食之际。远而至于天地神祗之尊。所以处之。莫不各有秩然之序灿然之文。接一物。必思卑已而不敢自尊。得一物。必思相让而不敢自有。无此性者非人也。夫智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周通之理以生。故其性为智。而其施于用也。察夫事之所当然则毫分缕析而不可乱。推其理之所以然则穷本极源而无不达。见人之所是而是之。虽在千古之上。而感激若亲睹。闻人之所非而非之。虽在四海之外。而忿疾若己病。无此性者非人也。夫信从何而来也。人得天地至实之理以生。故其性为信。而其施于用也。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接人必自尽。应物必以实。中孚足以及豚鱼。至诚足以感神明。无此性者非人也。此五者之于人道。若水之寒火之热。与生俱生。极天罔坠。故合而名之曰五常。以三纲大伦。经纬叙列斯人之类。而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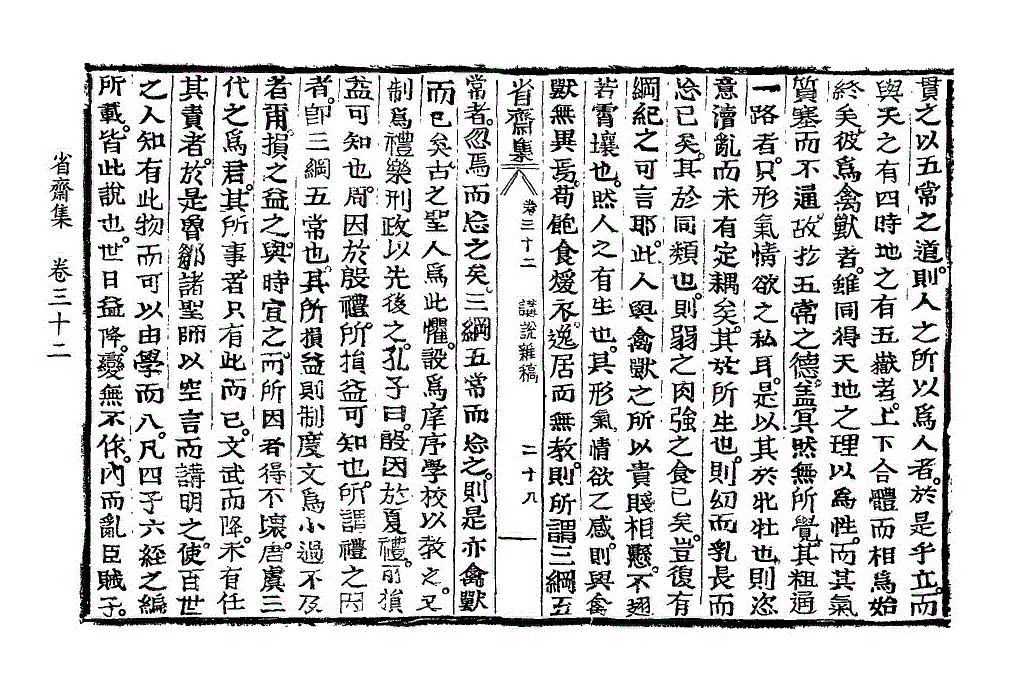 贯之以五常之道。则人之所以为人者。于是乎立。而与天之有四时地之有五岳者。上下合体而相为始终矣。彼为禽兽者。虽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而其气质塞而不通。故于五常之德。盖冥然无所觉。其粗通一路者。只形气情欲之私耳。是以其于牝牡也。则恣意渎乱而未有定耦矣。其于所生也。则幼而乳长而忘已矣。其于同类也。则弱之肉强之食已矣。岂复有纲纪之可言耶。此人与禽兽之所以贵贱相悬。不翅若霄壤也。然人之有生也。其形气情欲之感。则与禽兽无异焉。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所谓三纲五常者。忽焉而忘之矣。三纲五常而忘之。则是亦禽兽而已矣。古之圣人为此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又制为礼乐刑政以先后之。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谓礼之因者。即三纲五常也。其所损益则制度文为小过不及者尔。损之益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得不坏。唐虞三代之为君。其所事者只有此而已。文武而降。未有任其责者。于是鲁邹诸圣师以空言而讲明之。使百世之人知有此物而可以由学而入。凡四子六经之编所载。皆此说也。世日益降。变无不作。内而乱臣贼子。
贯之以五常之道。则人之所以为人者。于是乎立。而与天之有四时地之有五岳者。上下合体而相为始终矣。彼为禽兽者。虽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而其气质塞而不通。故于五常之德。盖冥然无所觉。其粗通一路者。只形气情欲之私耳。是以其于牝牡也。则恣意渎乱而未有定耦矣。其于所生也。则幼而乳长而忘已矣。其于同类也。则弱之肉强之食已矣。岂复有纲纪之可言耶。此人与禽兽之所以贵贱相悬。不翅若霄壤也。然人之有生也。其形气情欲之感。则与禽兽无异焉。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所谓三纲五常者。忽焉而忘之矣。三纲五常而忘之。则是亦禽兽而已矣。古之圣人为此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又制为礼乐刑政以先后之。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谓礼之因者。即三纲五常也。其所损益则制度文为小过不及者尔。损之益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得不坏。唐虞三代之为君。其所事者只有此而已。文武而降。未有任其责者。于是鲁邹诸圣师以空言而讲明之。使百世之人知有此物而可以由学而入。凡四子六经之编所载。皆此说也。世日益降。变无不作。内而乱臣贼子。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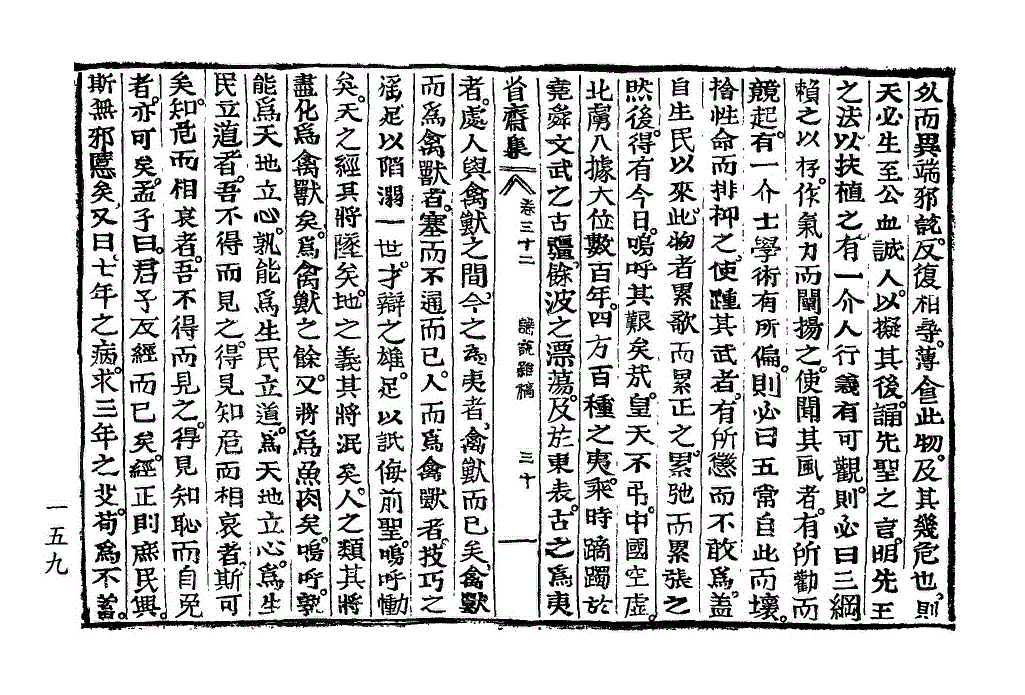 外而异端邪说。反复相寻。薄食此物。及其几危也。则天必生至公血诚人。以拟其后。诵先圣之言。明先王之法。以扶植之。有一介人行义有可观。则必曰三纲赖之以存。作气力而阐扬之。使闻其风者。有所劝而竞起。有一介士学术有所偏。则必曰五常自此而坏。舍性命而排抑之。使踵其武者。有所惩而不敢为。盖自生民以来。此物者累欹而累正之。累弛而累张之然后。得有今日。呜呼其艰矣哉。皇天不吊。中国空虚。北虏入据大位数百年。四方百种之夷。乘时蹢躅于尧舜文武之古疆。馀波之漂荡。及于东表。古之为夷者。处人与禽兽之间。今之为夷者。禽兽而已矣。禽兽而为禽兽者。塞而不通而已。人而为禽兽者。技巧之淫足以陷溺一世。才辩之雄。足以诋侮前圣。呜呼恸矣。天之经其将坠矣。地之义其将泯矣。人之类其将尽化为禽兽矣。为禽兽之馀。又将为鱼肉矣。呜呼。孰能为天地立心。孰能为生民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者。吾不得而见之。得见知危而相哀者。斯可矣。知危而相哀者。吾不得而见之。得见知耻而自免者。亦可矣。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又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
外而异端邪说。反复相寻。薄食此物。及其几危也。则天必生至公血诚人。以拟其后。诵先圣之言。明先王之法。以扶植之。有一介人行义有可观。则必曰三纲赖之以存。作气力而阐扬之。使闻其风者。有所劝而竞起。有一介士学术有所偏。则必曰五常自此而坏。舍性命而排抑之。使踵其武者。有所惩而不敢为。盖自生民以来。此物者累欹而累正之。累弛而累张之然后。得有今日。呜呼其艰矣哉。皇天不吊。中国空虚。北虏入据大位数百年。四方百种之夷。乘时蹢躅于尧舜文武之古疆。馀波之漂荡。及于东表。古之为夷者。处人与禽兽之间。今之为夷者。禽兽而已矣。禽兽而为禽兽者。塞而不通而已。人而为禽兽者。技巧之淫足以陷溺一世。才辩之雄。足以诋侮前圣。呜呼恸矣。天之经其将坠矣。地之义其将泯矣。人之类其将尽化为禽兽矣。为禽兽之馀。又将为鱼肉矣。呜呼。孰能为天地立心。孰能为生民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者。吾不得而见之。得见知危而相哀者。斯可矣。知危而相哀者。吾不得而见之。得见知耻而自免者。亦可矣。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又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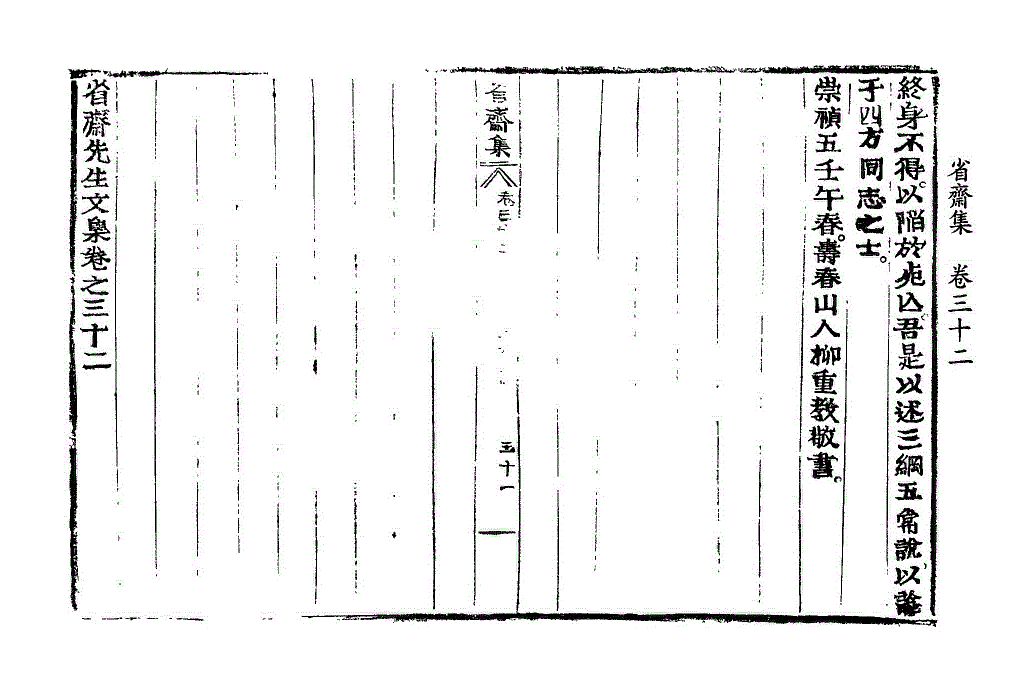 终身不得。以陷于死亡。吾是以述三纲五常说。以谂于四方同志之士。
终身不得。以陷于死亡。吾是以述三纲五常说。以谂于四方同志之士。崇祯五壬午春。寿春山人柳重教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