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往复杂稿
往复杂稿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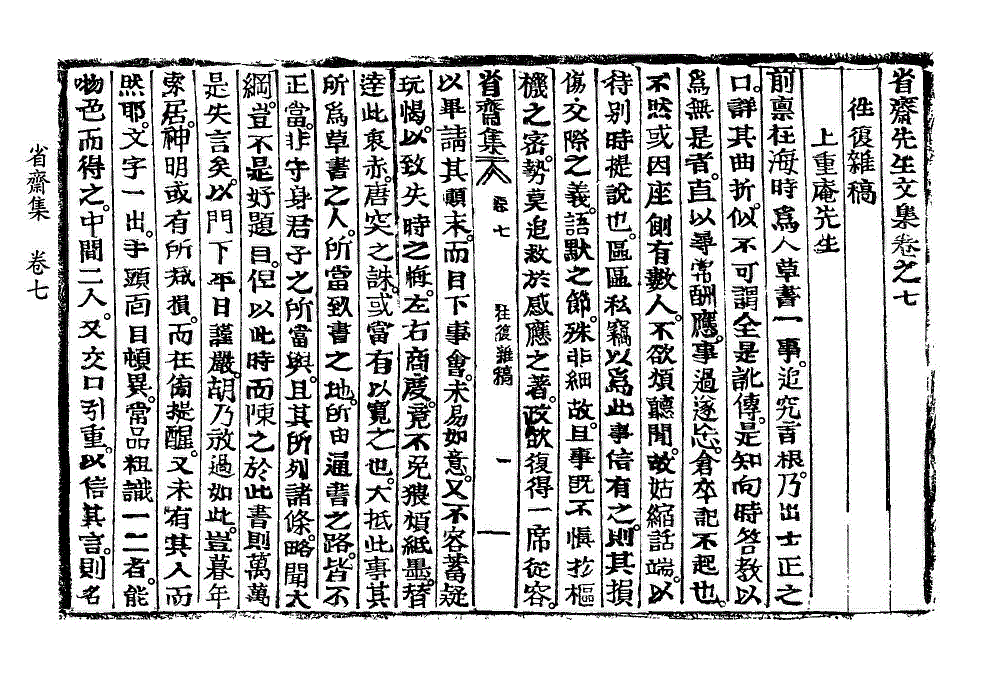 上重庵先生
上重庵先生前禀在海时为人草书一事。追究言根。乃出士正之口。详其曲折。似不可谓全是讹传。是知向时答教以为无是者。直以寻常酬应。事过遂忘。仓卒记不起也。不然或因座侧有数人。不欲烦听闻。故姑缩话端。以待别时提说也。区区私窃以为此事信有之。则其损伤交际之义。语默之节。殊非细故。且事既不慎于枢机之密。势莫追救于感应之著。政欲复得一席从容。以毕请其颠末。而目下事会。未易如意。又不容蓄疑玩愒。以致失时之悔。左右商度。竟不免猥烦纸墨。替达此衷赤。唐突之诛。或当有以宽之也。大抵此事其所为草书之人。所当致书之地。所由通书之路。皆不正当。非守身君子之所当与。且其所列诸条。略闻大纲。岂不是好题目。但以此时而陈之于此书则万万是失言矣。以门下平日谨严。胡乃放过如此。岂暮年索居。神明或有所减损。而在傍提醒。又未有其人而然耶。文字一出。手头面目顿异。常品粗识一二者。能物色而得之。中间二人。又交口引重。以信其言。则名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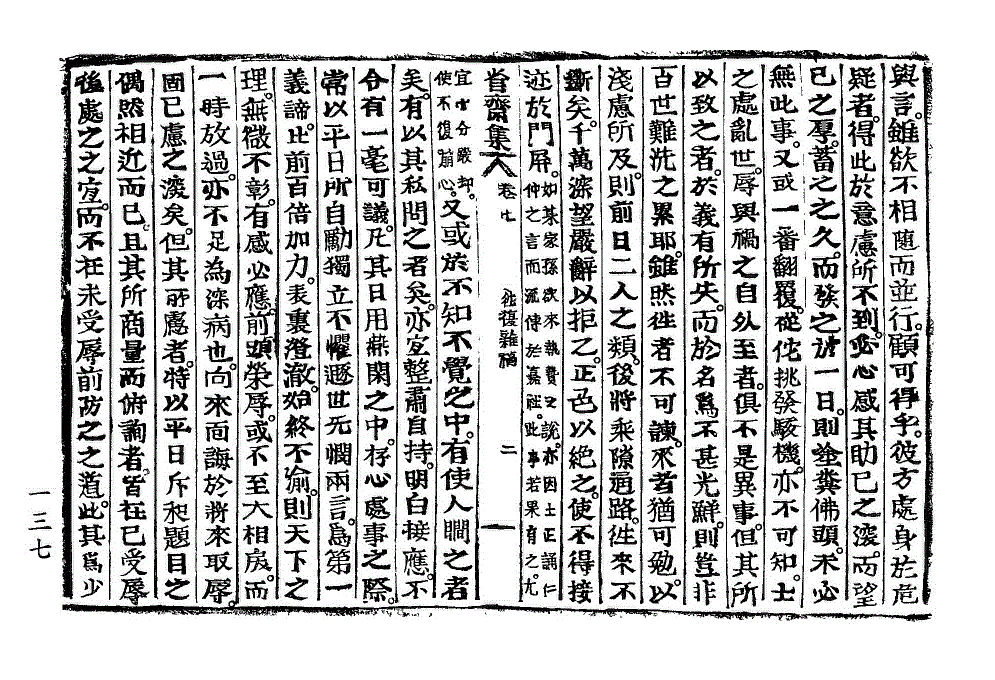 与言。虽欲不相随而并行。顾可得乎。彼方处身于危疑者。得此于意虑所不到。必心感其助己之深。而望己之厚。蓄之之久。而发之于一日。则涂粪佛头。未必无此事。又或一番翻覆。从佗挑发骇机。亦不可知。士之处乱世。辱与祸之自外至者。俱不是异事。但其所以致之者。于义有所失。而于名为不甚光鲜。则岂非百世难洗之累耶。虽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勉。以浅虑所及。则前日二人之类。后将乘隙通路。往来不断矣。千万深望严辞以拒之。正色以绝之。使不得接迹于门屏。(如某家孙欲来执贽之说。亦因士正诵仁仲之言而流传于嘉社。此事若果有之。尤宜十分严却。使不复萌心。)又或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使人瞷之者矣。有以其私问之者矣。亦宜整肃自持。明白接应。不令有一毫可议。凡其日用燕闲之中。存心处事之际。常以平日所自励独立不惧遁世无悯两言。为第一义谛。比前百倍加力。表里澄澈。始终不渝。则天下之理。无微不彰。有感必应。前头荣辱。或不至大相戾。而一时放过。亦不足为深病也。向来面诲于将来取辱。固已虑之深矣。但其所虑者。特以平日斥和题目之偶然相近而已。且其所商量而俯询者。皆在已受辱后处之之宜。而不在未受辱前防之之道。此其为少
与言。虽欲不相随而并行。顾可得乎。彼方处身于危疑者。得此于意虑所不到。必心感其助己之深。而望己之厚。蓄之之久。而发之于一日。则涂粪佛头。未必无此事。又或一番翻覆。从佗挑发骇机。亦不可知。士之处乱世。辱与祸之自外至者。俱不是异事。但其所以致之者。于义有所失。而于名为不甚光鲜。则岂非百世难洗之累耶。虽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勉。以浅虑所及。则前日二人之类。后将乘隙通路。往来不断矣。千万深望严辞以拒之。正色以绝之。使不得接迹于门屏。(如某家孙欲来执贽之说。亦因士正诵仁仲之言而流传于嘉社。此事若果有之。尤宜十分严却。使不复萌心。)又或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使人瞷之者矣。有以其私问之者矣。亦宜整肃自持。明白接应。不令有一毫可议。凡其日用燕闲之中。存心处事之际。常以平日所自励独立不惧遁世无悯两言。为第一义谛。比前百倍加力。表里澄澈。始终不渝。则天下之理。无微不彰。有感必应。前头荣辱。或不至大相戾。而一时放过。亦不足为深病也。向来面诲于将来取辱。固已虑之深矣。但其所虑者。特以平日斥和题目之偶然相近而已。且其所商量而俯询者。皆在已受辱后处之之宜。而不在未受辱前防之之道。此其为少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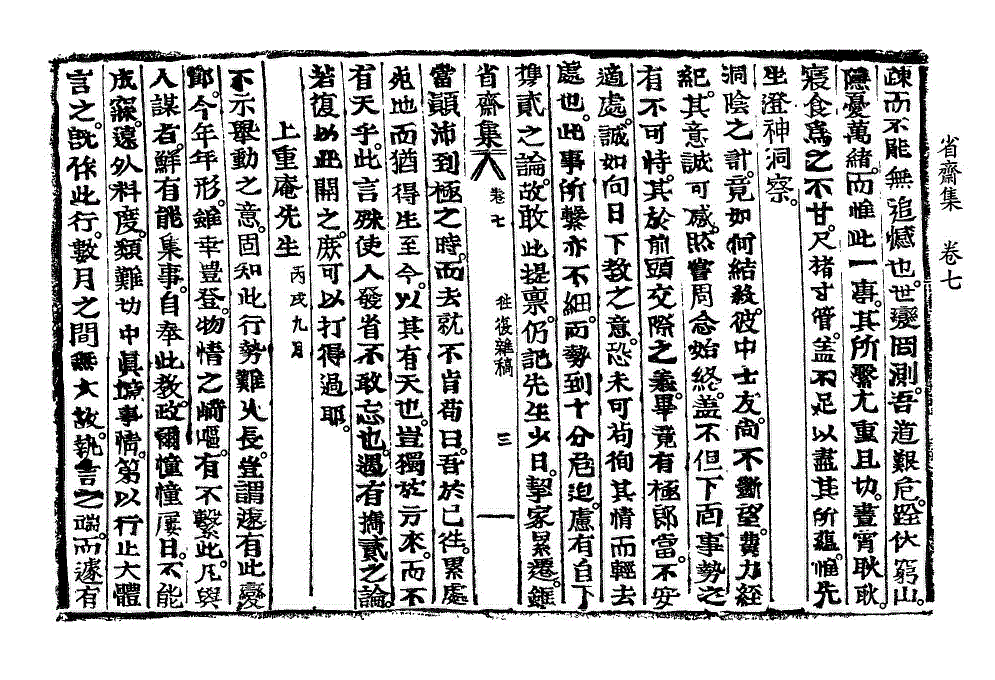 疏而不能无追憾也。世变罔测。吾道艰危。跧伏穷山。隐忧万绪。而惟此一事。其所系尤重且切。昼宵耿耿。寝食为之不甘。尺楮寸管。盖不足以尽其所蕴。惟先生澄神洞察。
疏而不能无追憾也。世变罔测。吾道艰危。跧伏穷山。隐忧万绪。而惟此一事。其所系尤重且切。昼宵耿耿。寝食为之不甘。尺楮寸管。盖不足以尽其所蕴。惟先生澄神洞察。洞阴之计。竟如何结杀。彼中士友。尚不断望。费力经纪。其意诚可感。然尝周念始终。盖不但下面事势之有不可恃。其于前头交际之义。毕竟有极郎当。不安适处。诚如向日下教之意。恐未可苟徇其情而轻去处也。此事所系亦不细。而势到十分危迫。虑有自下携贰之论。故敢此提禀。仍记先生少日。挈家累迁。虽当颠沛到极之时。而去就不肯苟曰。吾于已往。累处死地而犹得生至今。以其有天也。岂独于方来。而不有天乎。此言殊使人发省不敢忘也。遇有携贰之论。若复以此开之。庶可以打得过耶。
上重庵先生(丙戌九月)
下示举动之意。固知此行势难久长。岂谓遽有此变节。今年年形。虽幸礼登。物情之崎岖。有不系此。凡与人谋者。鲜有能集事。自奉此教。政尔憧憧屡日。不能成寐。远外料度。类难切中真境事情。第以行止大体言之。既作此行。数月之间无大故。执言之端。而遽有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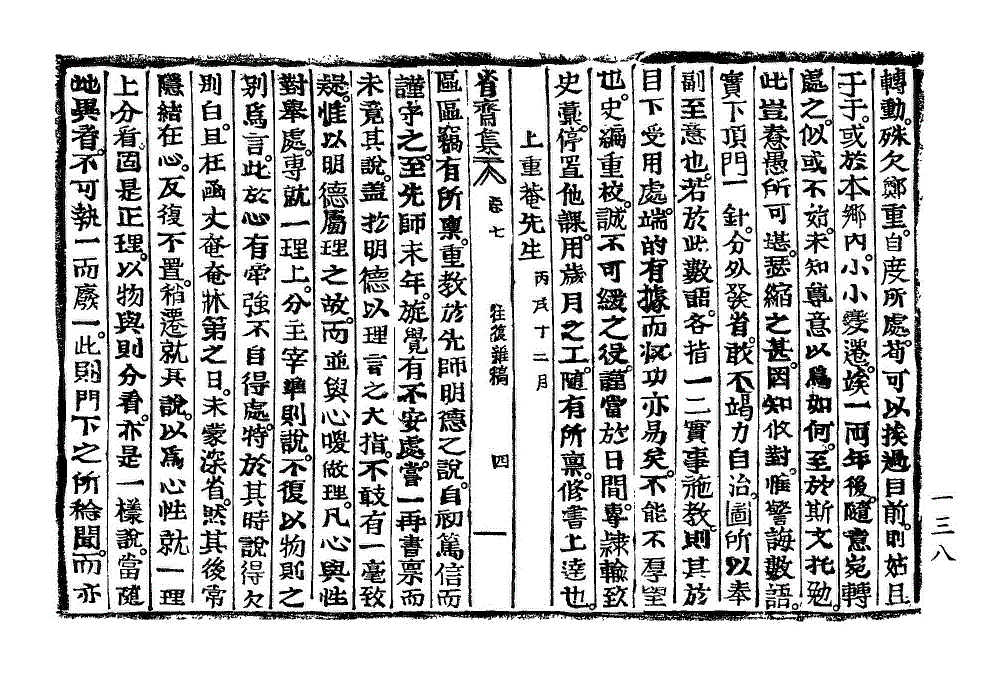 转动。殊欠郑重。自度所处。苟可以挨过目前。则姑且于于。或于本乡内。小小变迁。俟一两年后。随意宛转处之。似或不妨。未知尊意以为如何。至于斯文托勉。此岂憃愚所可堪。瑟缩之甚。罔知攸对。惟警诲数语。实下顶门一针。分外发省。敢不竭力自治。图所以奉副至意也。若于此数语。各指一二实事施教。则其于目下受用处。端的有据而收功亦易矣。不能不厚望也。史编重校。诚不可缓之役。谨当于日间。专隶输致史藁。停置他课。用岁月之工。随有所禀。修书上达也。
转动。殊欠郑重。自度所处。苟可以挨过目前。则姑且于于。或于本乡内。小小变迁。俟一两年后。随意宛转处之。似或不妨。未知尊意以为如何。至于斯文托勉。此岂憃愚所可堪。瑟缩之甚。罔知攸对。惟警诲数语。实下顶门一针。分外发省。敢不竭力自治。图所以奉副至意也。若于此数语。各指一二实事施教。则其于目下受用处。端的有据而收功亦易矣。不能不厚望也。史编重校。诚不可缓之役。谨当于日间。专隶输致史藁。停置他课。用岁月之工。随有所禀。修书上达也。上重庵先生(丙戌十二月)
区区窃有所禀。重教于先师明德之说。自初笃信而谨守之。至先师末年。旋觉有不安处。尝一再书禀而未竟其说。盖于明德以理言之大指。不敢有一毫致疑。惟以明德属理之故。而并与心唤做理。凡心与性对举处。专就一理上。分主宰准则说。不复以物则之别为言。此于心有牵强不自得处。特于其时说得欠别白。且在函丈奄奄床笫之日。未蒙深省。然其后常隐结在心。反复不置。稍迁就其说。以为心性就一理上分看。固是正理。以物与则分看。亦是一样说。当随地异看。不可执一而废一。此则门下之所稔闻。而亦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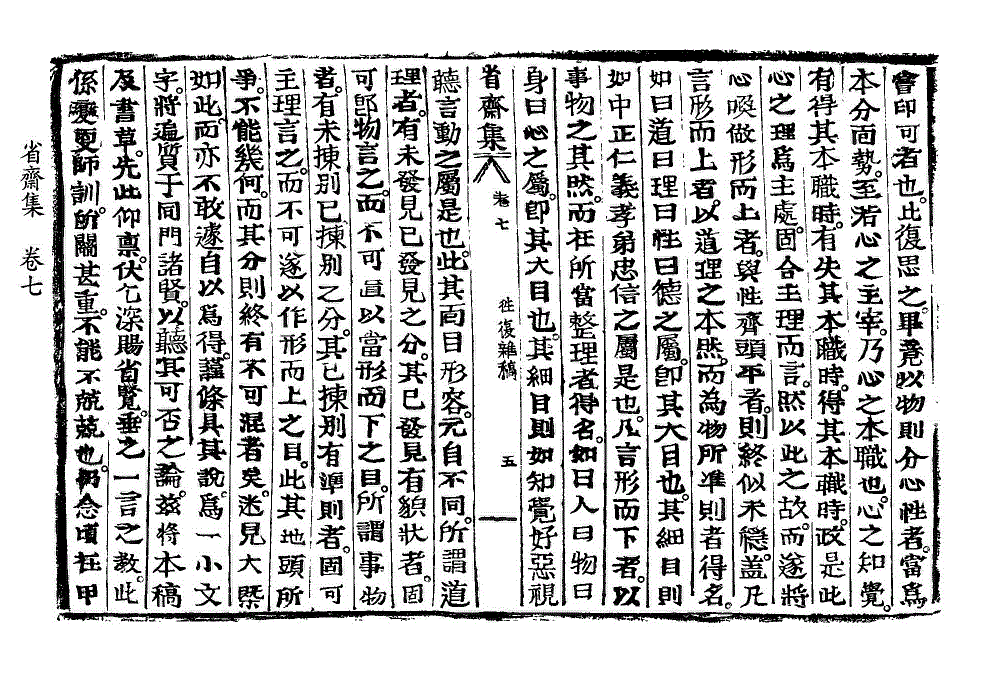 尝印可者也。比复思之。毕竟以物则分心性者。当为本分面势。至若心之主宰。乃心之本职也。心之知觉。有得其本职时。有失其本职时。得其本职时。政是此心之理为主处。固合主理而言。然以此之故。而遂将心唤做形而上者。与性齐头平看。则终似未稳。盖凡言形而上者。以道理之本然。而为物所准则者得名。如曰道曰理曰性曰德之属。即其大目也。其细目则如中正仁义孝弟忠信之属是也。凡言形而下者。以事物之其然。而在所当整理者得名。如曰人曰物曰身曰心之属。即其大目也。其细目则如知觉好恶视听言动之属是也。此其面目形容。元自不同。所谓道理者。有未发见已发见之分。其已发见有貌状者。固可即物言之。而不可直以当形而下之目。所谓事物者。有未拣别已拣别之分。其已拣别有准则者。固可主理言之。而不可遂以作形而上之目。此其地头所争。不能几何。而其分则终有不可混者矣。迷见大槩如此。而亦不敢遽自以为得。谨条具其说。为一小文字。将遍质于同门诸贤。以听其可否之论。玆将本稿及书草。先此仰禀。伏乞深赐省览。垂之一言之教。此系变更师训。所关甚重。不能不兢兢也。仍念顷在甲
尝印可者也。比复思之。毕竟以物则分心性者。当为本分面势。至若心之主宰。乃心之本职也。心之知觉。有得其本职时。有失其本职时。得其本职时。政是此心之理为主处。固合主理而言。然以此之故。而遂将心唤做形而上者。与性齐头平看。则终似未稳。盖凡言形而上者。以道理之本然。而为物所准则者得名。如曰道曰理曰性曰德之属。即其大目也。其细目则如中正仁义孝弟忠信之属是也。凡言形而下者。以事物之其然。而在所当整理者得名。如曰人曰物曰身曰心之属。即其大目也。其细目则如知觉好恶视听言动之属是也。此其面目形容。元自不同。所谓道理者。有未发见已发见之分。其已发见有貌状者。固可即物言之。而不可直以当形而下之目。所谓事物者。有未拣别已拣别之分。其已拣别有准则者。固可主理言之。而不可遂以作形而上之目。此其地头所争。不能几何。而其分则终有不可混者矣。迷见大槩如此。而亦不敢遽自以为得。谨条具其说。为一小文字。将遍质于同门诸贤。以听其可否之论。玆将本稿及书草。先此仰禀。伏乞深赐省览。垂之一言之教。此系变更师训。所关甚重。不能不兢兢也。仍念顷在甲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39L 页
 寅乙卯间。门下从洛下归。将心说异同。书禀先师。连章累牍而不之止。此时从傍参观。政合有一番深思。而缘见识未能及此。只管主张前说。左右防遮。以固师门之志。逮夫既晚而后。乃有此云云。而俯仰今昔。便成千古之恨。追阅当时往复之迹。未尝不为之慨然也。
寅乙卯间。门下从洛下归。将心说异同。书禀先师。连章累牍而不之止。此时从傍参观。政合有一番深思。而缘见识未能及此。只管主张前说。左右防遮。以固师门之志。逮夫既晚而后。乃有此云云。而俯仰今昔。便成千古之恨。追阅当时往复之迹。未尝不为之慨然也。上重庵先生(丙戌十二月二十四日)
日前徐复卿之来。乘间与坐。问及近日师门调过节度。乃言九月间。门下人沈稚浚。以丈席乏食欲动之意。告于金相公家。得十包谷。以契谷为名而进之。以此挨过目前。而其事甚閟。门下人知之者。只一二人耳。重教闻甚惊骇。而事在隐密。且属既往。有难干预其曲折。故只得详告其大未安之意于徐君而止矣。追后思之。终是悚懔。有不能自已者。遂作一书于沈君。以深警切之。冀其或有救于后也。书成未发而族生重岳适至。言其里人近自永平归。亦云金公十包之馈。乡传颇藉藉。于是遂与重岳相对忧叹。以为金公固是负一国清望。弃官乡居。萧然若寒士。而比之先生之岩穴一布衣。则情迹犹相远。且于平日。曾未有游从之实。只于奠居之初。一次来见而已。以此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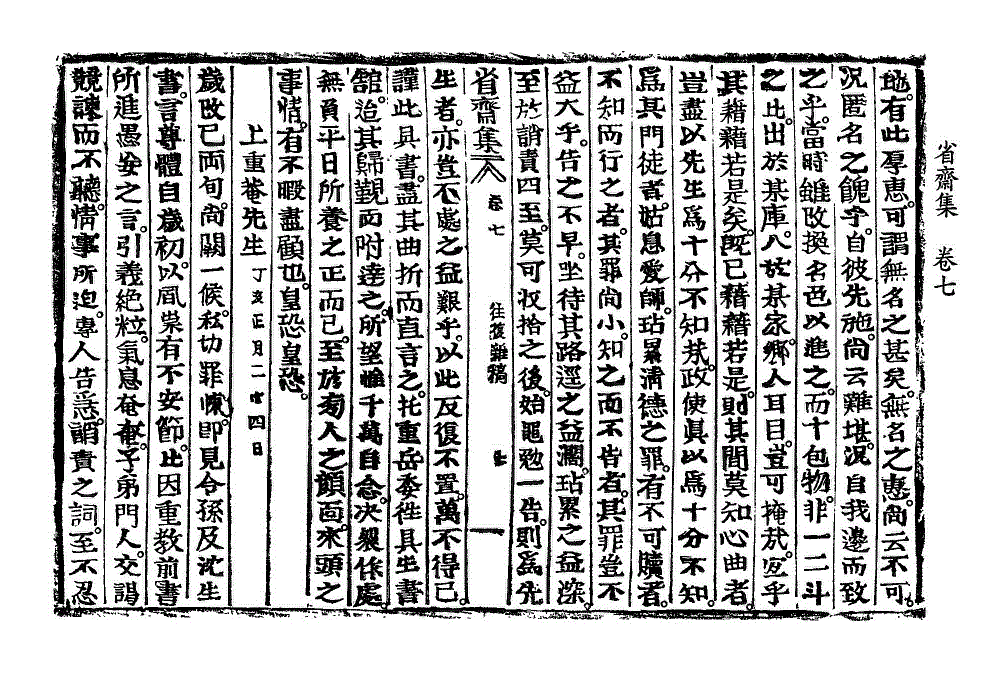 地。有此厚惠。可谓无名之甚矣。无名之惠。尚云不可。况匿名之馈乎。自彼先施。尚云难堪。况自我边而致之乎。当时虽改换名色以进之。而十包物。非一二斗之比。出于某库。入于某家。乡人耳目。岂可掩哉。宜乎其藉藉若是矣。既已藉藉若是。则其间莫知心曲者。岂尽以先生为十分不知哉。政使真以为十分不知。为其门徒者。姑息爱师。玷累清德之罪。有不可赎者。不知而行之者。其罪尚小。知之而不告者。其罪岂不益大乎。告之不早。坐待其路径之益阔。玷累之益深。至于诮责四至。莫可收拾之后。始黾勉一告。则为先生者。亦岂不处之益艰乎。以此反复不置。万不得已。谨此具书。尽其曲折而直言之。托重岳委往具生书馆。迨其归觐而附达之。所望惟千万自念。决裂作处。无负平日所养之正而已。至于旁人之颜面。来头之事情。有不暇尽顾也。皇恐皇恐。
地。有此厚惠。可谓无名之甚矣。无名之惠。尚云不可。况匿名之馈乎。自彼先施。尚云难堪。况自我边而致之乎。当时虽改换名色以进之。而十包物。非一二斗之比。出于某库。入于某家。乡人耳目。岂可掩哉。宜乎其藉藉若是矣。既已藉藉若是。则其间莫知心曲者。岂尽以先生为十分不知哉。政使真以为十分不知。为其门徒者。姑息爱师。玷累清德之罪。有不可赎者。不知而行之者。其罪尚小。知之而不告者。其罪岂不益大乎。告之不早。坐待其路径之益阔。玷累之益深。至于诮责四至。莫可收拾之后。始黾勉一告。则为先生者。亦岂不处之益艰乎。以此反复不置。万不得已。谨此具书。尽其曲折而直言之。托重岳委往具生书馆。迨其归觐而附达之。所望惟千万自念。决裂作处。无负平日所养之正而已。至于旁人之颜面。来头之事情。有不暇尽顾也。皇恐皇恐。上重庵先生(丁亥正月二十四日)
岁改已两旬。尚阙一候。私切罪悚。即见令孙及沈生书。言尊体自岁初。以风祟有不安节。比因重教前书所进愚妄之言。引义绝粒。气息奄奄。子弟门人。交谒竞谏而不听。情事所迫。专人告急。诮责之词。至不忍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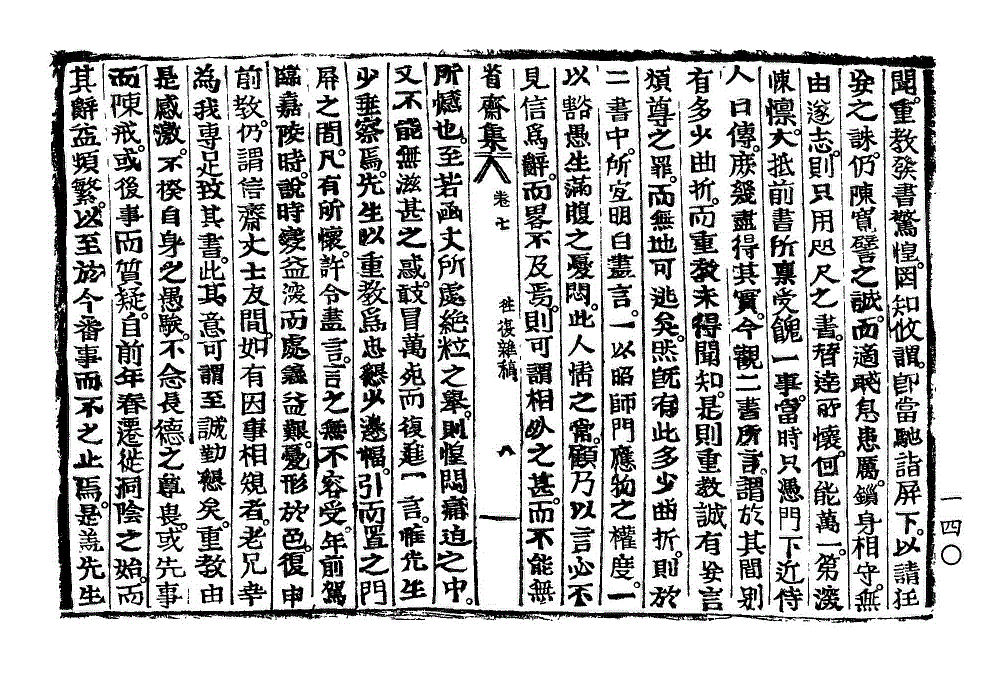 闻。重教发书惊惶。罔知攸谓。即当驰诣屏下。以请狂妄之诛。仍陈宽譬之诚。而适贱息患厉。锁身相守。无由遂志。则只用咫尺之书。替达所怀。何能万一。第深悚懔。大抵前书所禀受馈一事。当时只凭门下近侍人曰传。庶几尽得其实。今观二书所言。谓于其间别有多少曲折。而重教未得闻知。是则重教诚有妄言烦尊之罪。而无地可逃矣。然既有此多少曲折。则于二书中。所宜明白尽言。一以昭师门应物之权度。一以豁愚生满腹之忧闷。此人情之常。顾乃以言必不见信为辞。而略不及焉。则可谓相外之甚。而不能无所憾也。至若函丈所处绝粒之举。则惶闷痛迫之中。又不能无滋甚之惑。敢冒万死而复进一言。惟先生少垂察焉。先生以重教为忠恳少边幅。引而置之门屏之间。凡有所怀。许令尽言。言之无不容受。年前驾临嘉陵时。说时变益深而处义益艰。忧形于色。复申前教。仍谓信斋丈士友间。如有因事相规者。老兄幸为我专足致其书。此其意可谓至诚勤恳矣。重教由是感激。不揆自身之愚騃。不念长德之尊畏。或先事而陈戒。或后事而质疑。自前年春迁徙洞阴之始。而其辞益频繁。以至于今番事而不之止焉。是盖先生
闻。重教发书惊惶。罔知攸谓。即当驰诣屏下。以请狂妄之诛。仍陈宽譬之诚。而适贱息患厉。锁身相守。无由遂志。则只用咫尺之书。替达所怀。何能万一。第深悚懔。大抵前书所禀受馈一事。当时只凭门下近侍人曰传。庶几尽得其实。今观二书所言。谓于其间别有多少曲折。而重教未得闻知。是则重教诚有妄言烦尊之罪。而无地可逃矣。然既有此多少曲折。则于二书中。所宜明白尽言。一以昭师门应物之权度。一以豁愚生满腹之忧闷。此人情之常。顾乃以言必不见信为辞。而略不及焉。则可谓相外之甚。而不能无所憾也。至若函丈所处绝粒之举。则惶闷痛迫之中。又不能无滋甚之惑。敢冒万死而复进一言。惟先生少垂察焉。先生以重教为忠恳少边幅。引而置之门屏之间。凡有所怀。许令尽言。言之无不容受。年前驾临嘉陵时。说时变益深而处义益艰。忧形于色。复申前教。仍谓信斋丈士友间。如有因事相规者。老兄幸为我专足致其书。此其意可谓至诚勤恳矣。重教由是感激。不揆自身之愚騃。不念长德之尊畏。或先事而陈戒。或后事而质疑。自前年春迁徙洞阴之始。而其辞益频繁。以至于今番事而不之止焉。是盖先生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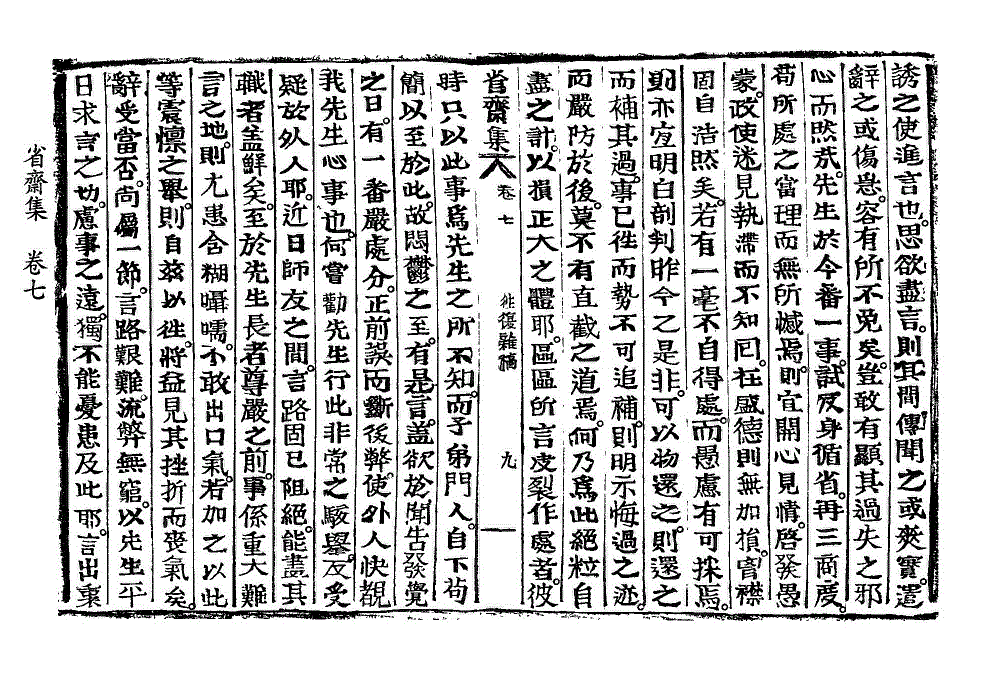 诱之使进言也。思欲尽言。则其间传闻之或爽实。遣辞之或伤急。容有所不免矣。岂敢有显其过失之邪心而然哉。先生于今番一事。试反身循省。再三商度。苟所处之当理而无所憾焉。则宜开心见情。启发愚蒙。政使迷见执滞而不知回。在盛德则无加损。胸襟固自浩然矣。若有一毫不自得处。而愚虑有可采焉。则亦宜明白剖判昨今之是非。可以物还之。则还之而补其过。事已往而势不可追补。则明示悔过之迹。而严防于后。莫不有直截之道焉。何乃为此绝粒自尽之计。以损正大之体耶。区区所言决裂作处者。彼时只以此事为先生之所不知。而子弟门人。自下苟简以至于此。故闷郁之至。有是言。盖欲于闻告发觉之日。有一番严处分。正前误而断后㢢。使外人快睹我先生心事也。何尝劝先生行此非常之骇举。反受疑于外人耶。近日师友之间。言路固已阻绝。能尽其职者盖鲜矣。至于先生长者尊严之前。事系重大难言之地。则尤患含糊嗫嚅。不敢出口气。若加之以此等震懔之举。则自玆以往。将益见其挫折而丧气矣。辞受当否。尚属一节。言路艰难。流弊无穷。以先生平日求言之切。虑事之远。独不能忧患及此耶。言出衷
诱之使进言也。思欲尽言。则其间传闻之或爽实。遣辞之或伤急。容有所不免矣。岂敢有显其过失之邪心而然哉。先生于今番一事。试反身循省。再三商度。苟所处之当理而无所憾焉。则宜开心见情。启发愚蒙。政使迷见执滞而不知回。在盛德则无加损。胸襟固自浩然矣。若有一毫不自得处。而愚虑有可采焉。则亦宜明白剖判昨今之是非。可以物还之。则还之而补其过。事已往而势不可追补。则明示悔过之迹。而严防于后。莫不有直截之道焉。何乃为此绝粒自尽之计。以损正大之体耶。区区所言决裂作处者。彼时只以此事为先生之所不知。而子弟门人。自下苟简以至于此。故闷郁之至。有是言。盖欲于闻告发觉之日。有一番严处分。正前误而断后㢢。使外人快睹我先生心事也。何尝劝先生行此非常之骇举。反受疑于外人耶。近日师友之间。言路固已阻绝。能尽其职者盖鲜矣。至于先生长者尊严之前。事系重大难言之地。则尤患含糊嗫嚅。不敢出口气。若加之以此等震懔之举。则自玆以往。将益见其挫折而丧气矣。辞受当否。尚属一节。言路艰难。流弊无穷。以先生平日求言之切。虑事之远。独不能忧患及此耶。言出衷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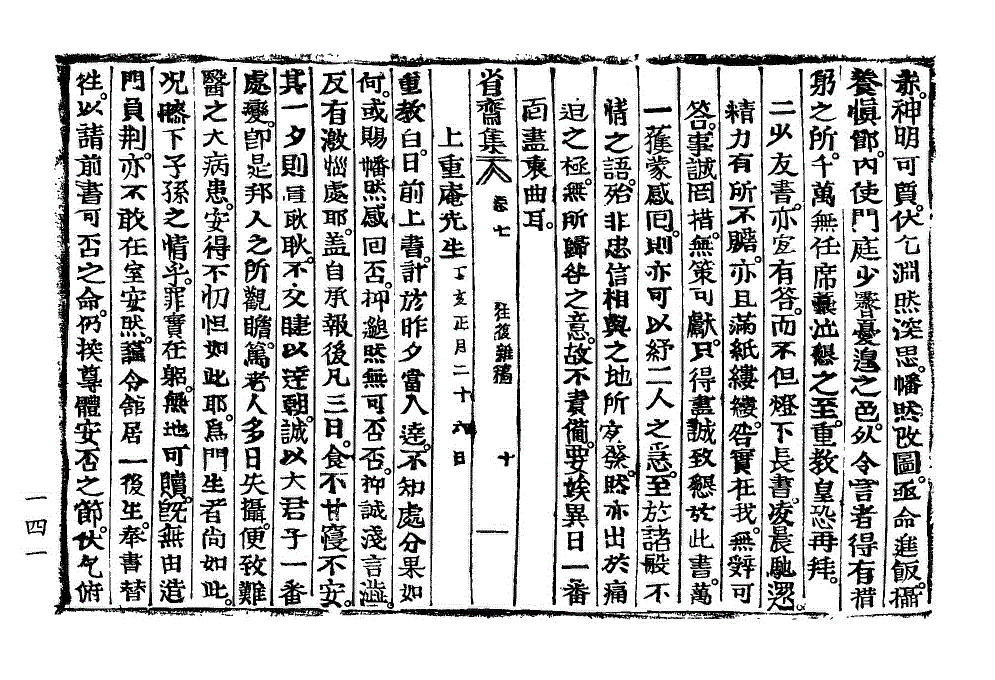 赤。神明可质。伏乞渊然深思。幡然改图。亟命进饭。摄养慎节。内使门庭少霁忧遑之色。外令言者得有措躬之所。千万无任席藁泣恳之至。重教皇恐再拜。
赤。神明可质。伏乞渊然深思。幡然改图。亟命进饭。摄养慎节。内使门庭少霁忧遑之色。外令言者得有措躬之所。千万无任席藁泣恳之至。重教皇恐再拜。二少友书。亦宜有答。而不但灯下长书。凌晨驰还。精力有所不赡。亦且满纸缕缕。咎实在我。无辞可答。事诚罔措。无策可献。只得尽诚致恳于此书。万一获蒙感回。则亦可以纾二人之急。至于诸般不情之语。殆非忠信相与之地所宜发。然亦出于痛迫之极。无所归咎之意。故不责备。要俟异日一番面尽衷曲耳。
上重庵先生(丁亥正月二十六日)
重教白。日前上书。计于昨夕当入达。不知处分果如何。或赐幡然感回否。抑邈然无可否否。抑诚浅言涩。反有激恼处耶。盖自承报后凡三日。食不甘寝不安。其一夕则直耿耿。不交睫以达朝。诚以大君子一番处变。即是邦人之所观瞻。笃老人多日失摄。便致难医之大病患。安得不忉怛如此耶。为门生者尚如此。况膝下子孙之情乎。罪实在躬。无地可赎。既无由造门负荆。亦不敢在室安然。谨令馆居一后生。奉书替往。以请前书可否之命。仍探尊体安否之节。伏乞俯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2H 页
 察微诚。少降气色。虽在床笫奄奄之中。呼倩数语。以示德意。则不翅若大旱之得甘霈。千万无任顿首祈祝之至。重教皇恐再拜。
察微诚。少降气色。虽在床笫奄奄之中。呼倩数语。以示德意。则不翅若大旱之得甘霈。千万无任顿首祈祝之至。重教皇恐再拜。别纸(二条一条未录)
万万皇悚中。窃有一事冒昧烦禀者。谨考令孙及沈生书本。于贱身有多少不情之语不忍提说者。然此即小生平日诚意不见孚之致。只得自反而已。不敢屑屑为分疏计。至于从前有三数人。持先生之短者。闻甚骇痛。而不知所指的是何人。当从后根覈其人。痛惩恶习。惟于今番事。行吹觅谮愬之习者。追思前日以此事上书时。有重岳一人在傍参论。于书中亦有提及处。是指此人而言之耶。若尔则其时事状。有可为仰诵者。盖于此时重教只因徐生。详闻此事里面曲折。而不知外间传播已如彼。重岳只凭里人。略闻外间传播。而不知里面曲折乃如此。及其偶然相聚。不得不同声忧叹。重教以为此事只出在下人手势。而先生未之知。则合有一番直达。以听其自行作处。乃得救正。重岳以为在吾辈处义。惟此一事为可以效忠耳。及其书成。无便可付。重岳时以妻病。方作求药之行。以为事有轻重。时不可缓。遂自请往具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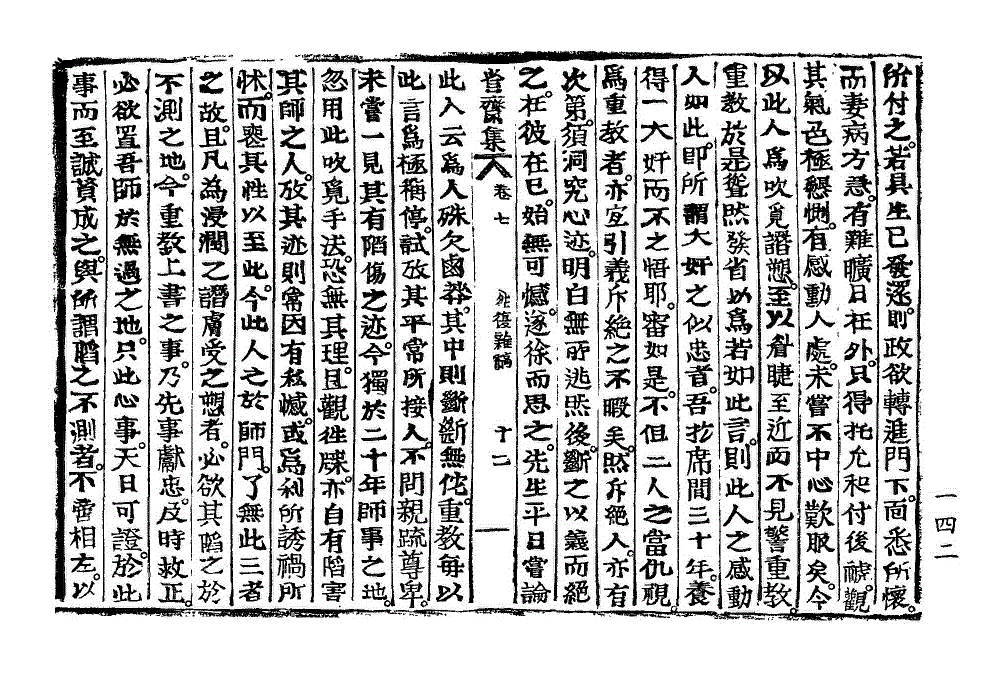 所付之。若具生已发还。则政欲转进门下。面悉所怀。而妻病方急。有难旷日在外。只得托允和付后褫。观其气色极恳恻。有感动人处。未尝不中心叹服矣。今以此人为吹觅谮愬。至以眉睫至近而不见警重教。重教于是耸然发省以为若如此言。则此人之感动人如此。即所谓大奸之似忠者。吾于席间三十年。养得一大奸而不之悟耶。审如是。不但二人之当仇视。为重教者。亦宜引义斥绝之不暇矣。然斥绝人。亦有次第。须洞究心迹。明白无所逃然后。断之以义而绝之。在彼在己。始无可憾。遂徐而思之。先生平日尝论此人云为人殊欠卤莽。其中则断断无佗。重教每以此言为极称停。试考其平常所接人。不问亲疏尊卑。未尝一见其有陷伤之迹。今独于二十年师事之地。忽用此吹觅手法。恐无其理。且观往牒。亦自有陷害其师之人。考其迹则常因有私憾。或为利所诱祸所怵。而丧其性以至此。今此人之于师门。了无此三者之故。且凡为浸润之谮肤受之愬者。必欲其陷之于不测之地。今重教上书之事。乃先事献忠。及时救正。必欲置吾师于无过之地。只此心事。天日可證。于此事而至诚赞成之。与所谓陷之不测者。不啻相左。以
所付之。若具生已发还。则政欲转进门下。面悉所怀。而妻病方急。有难旷日在外。只得托允和付后褫。观其气色极恳恻。有感动人处。未尝不中心叹服矣。今以此人为吹觅谮愬。至以眉睫至近而不见警重教。重教于是耸然发省以为若如此言。则此人之感动人如此。即所谓大奸之似忠者。吾于席间三十年。养得一大奸而不之悟耶。审如是。不但二人之当仇视。为重教者。亦宜引义斥绝之不暇矣。然斥绝人。亦有次第。须洞究心迹。明白无所逃然后。断之以义而绝之。在彼在己。始无可憾。遂徐而思之。先生平日尝论此人云为人殊欠卤莽。其中则断断无佗。重教每以此言为极称停。试考其平常所接人。不问亲疏尊卑。未尝一见其有陷伤之迹。今独于二十年师事之地。忽用此吹觅手法。恐无其理。且观往牒。亦自有陷害其师之人。考其迹则常因有私憾。或为利所诱祸所怵。而丧其性以至此。今此人之于师门。了无此三者之故。且凡为浸润之谮肤受之愬者。必欲其陷之于不测之地。今重教上书之事。乃先事献忠。及时救正。必欲置吾师于无过之地。只此心事。天日可證。于此事而至诚赞成之。与所谓陷之不测者。不啻相左。以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3H 页
 此而得此目。终或称冤。反复推之。未得安贴处。亦不敢以私智断定。谨此仰禀。不识先生于此人。果何以处之。若以为奸而与前日所恃断断者相反。则勿以事关自己为嫌。明白垂示其意。重教谨当依其意。一番猛省。求所以处之之道。如曰不然。而只出二人一时无所归咎之辞。则亦望一番开谕二人。毋至留滞作胸中一物。是乃盛德事也。未知如何。后生书中句语。初不必仰烦尊听而辨别人邪正。系是格致之一端。黜陟一生徒。亦是门下之大事。早晚亦须有关听。故如是奉禀焉。主臣主臣。
此而得此目。终或称冤。反复推之。未得安贴处。亦不敢以私智断定。谨此仰禀。不识先生于此人。果何以处之。若以为奸而与前日所恃断断者相反。则勿以事关自己为嫌。明白垂示其意。重教谨当依其意。一番猛省。求所以处之之道。如曰不然。而只出二人一时无所归咎之辞。则亦望一番开谕二人。毋至留滞作胸中一物。是乃盛德事也。未知如何。后生书中句语。初不必仰烦尊听而辨别人邪正。系是格致之一端。黜陟一生徒。亦是门下之大事。早晚亦须有关听。故如是奉禀焉。主臣主臣。上重庵先生
重教白。累日延颈之馀。高生奉书而还。再拜启函。谨审其间寝膳复常。体内安康。勉赐手诲。警责鼎重。副以口教。曲折备至。此可以仰体不忍终弃。俾得自新之盛意。且感且悚。伏地顿首。罔知所以为谢也。重教所犯罪过。前书所陈妄言烦尊无所逃罪之语。传闻爽实遣辞伤急之句。固已略见其自引之情。特是书主言绝粒事未安。辞繁意乱。为其所掩耳。今始检之。急于进谏而忽于反省。详于原情而缓于引咎。果又犯责上责下中自恕己之罪。而下教及此。不觉惶汗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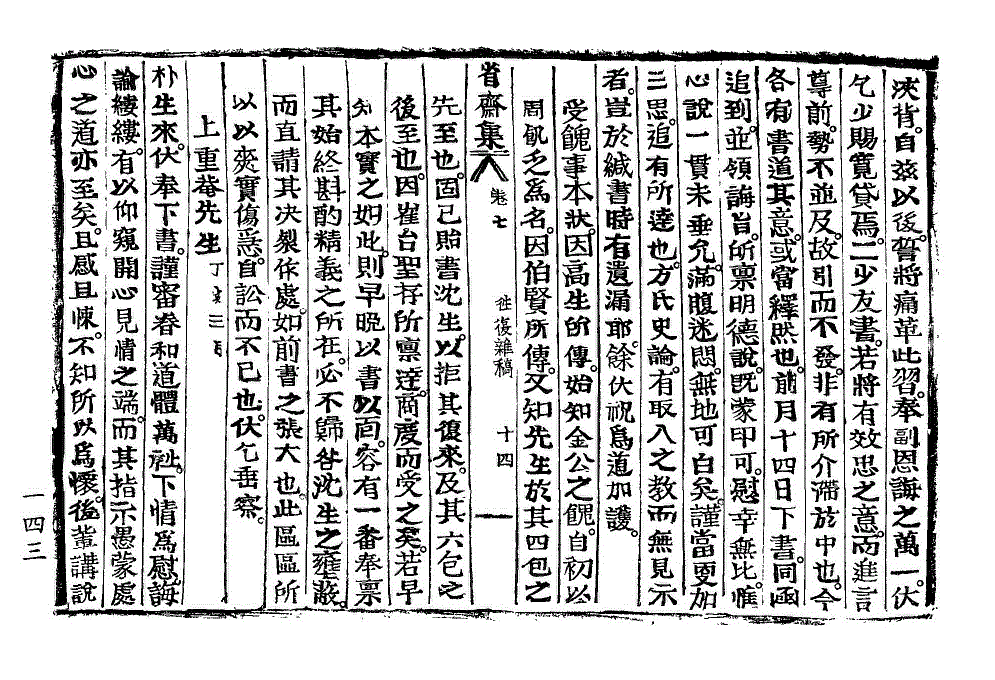 浃背。自玆以后。誓将痛革此习。奉副恩诲之万一。伏乞少赐宽贷焉。二少友书。若将有效忠之意。而进言尊前。势不并及。故引而不发。非有所介滞于中也。今各有书道其意。或当释然也。前月十四日下书。同函追到。并领诲旨。所禀明德说。既蒙印可。慰幸无比。惟心说一贯未垂允。满腹迷闷。无地可白矣。谨当更加三思。追有所达也。方氏史论。有取入之教而无见示者。岂于缄书时有遗漏耶。馀伏祝为道加护。
浃背。自玆以后。誓将痛革此习。奉副恩诲之万一。伏乞少赐宽贷焉。二少友书。若将有效忠之意。而进言尊前。势不并及。故引而不发。非有所介滞于中也。今各有书道其意。或当释然也。前月十四日下书。同函追到。并领诲旨。所禀明德说。既蒙印可。慰幸无比。惟心说一贯未垂允。满腹迷闷。无地可白矣。谨当更加三思。追有所达也。方氏史论。有取入之教而无见示者。岂于缄书时有遗漏耶。馀伏祝为道加护。受馈事本状。因高生所传。始知金公之馈。自初以周饥乏为名。因伯贤所传。又知先生于其四包之先至也。固已贻书沈生。以拒其复来。及其六包之后至也。因崔台圣存所禀达。商度而受之矣。若早知本实之如此。则早晚以书以面。容有一番奉禀其始终斟酌精义之所在。必不归咎沈生之壅蔽。而直请其决裂作处。如前书之张大也。此区区所以以爽实伤急。自讼而不已也。伏乞垂察。
上重庵先生(丁亥三月)
朴生来。伏奉下书。谨审春和道体万祉。下情为慰。诲谕缕缕。有以仰窥开心见情之端。而其指示愚蒙处心之道亦至矣。且感且悚。不知所以为怀。后辈讲说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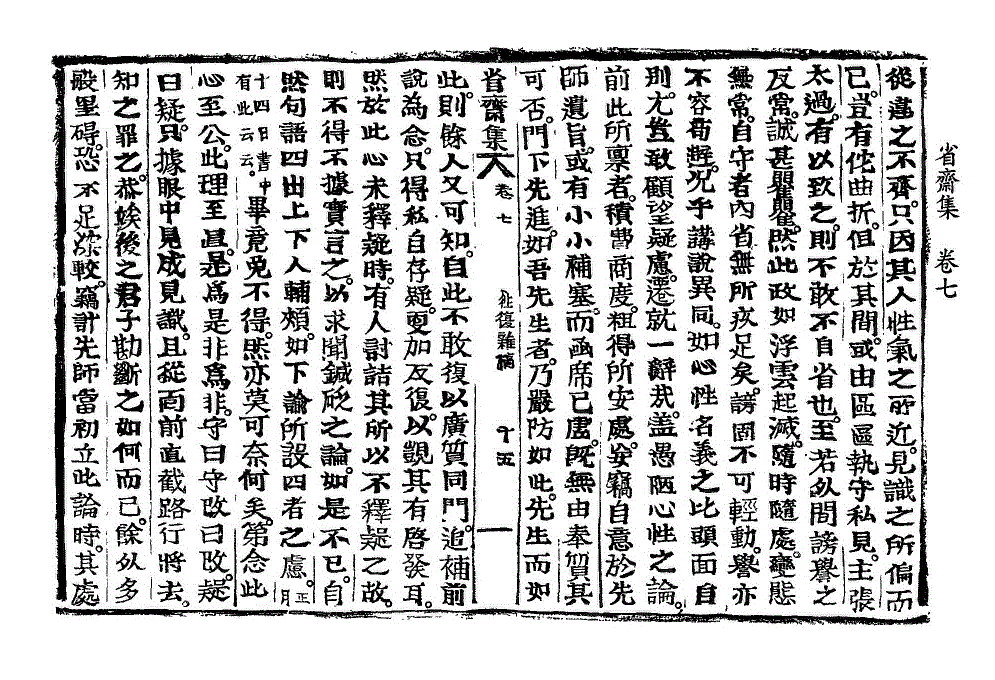 从违之不齐。只因其人性气之所近。见识之所偏而已。岂有佗曲折。但于其间。或由区区执守私见。主张太过。有以致之。则不敢不自省也。至若外间谤誉之反常。诚甚瞿瞿。然此政如浮云起灭。随时随处。变态无常。自守者内省无所疚足矣。谤固不可轻动。誉亦不容苟避。况乎讲说异同。如心性名义之比头面自别。尤岂敢顾望疑虑。迁就一辞哉。盖愚陋心性之论。前此所禀者。积费商度。粗得所安处。妄窃自意于先师遗旨。或有小小补塞。而函席已虚。既无由奉质其可否。门下先进。如吾先生者。乃严防如此。先生而如此。则馀人又可知。自此不敢复以广质同门。追补前说为念。只得私自存疑。更加反复。以觊其有启发耳。然于此心未释疑时。有人讨诘其所以不释疑之故。则不得不据实言之。以求闻针砭之论。如是不已。自然句语四出上下人辅颊。如下谕所设四者之虑。(正月十四日书中有此云云。)毕竟免不得。然亦莫可奈何矣。第念此心至公。此理至直。是为是非为非。守曰守改曰改。疑曰疑。只据眼中见成见识。且从面前直截路行将去。知之罪之。恭俟后之君子勘断之如何而已。馀外多般挂碍。恐不足深较。窃计先师当初立此论时。其处
从违之不齐。只因其人性气之所近。见识之所偏而已。岂有佗曲折。但于其间。或由区区执守私见。主张太过。有以致之。则不敢不自省也。至若外间谤誉之反常。诚甚瞿瞿。然此政如浮云起灭。随时随处。变态无常。自守者内省无所疚足矣。谤固不可轻动。誉亦不容苟避。况乎讲说异同。如心性名义之比头面自别。尤岂敢顾望疑虑。迁就一辞哉。盖愚陋心性之论。前此所禀者。积费商度。粗得所安处。妄窃自意于先师遗旨。或有小小补塞。而函席已虚。既无由奉质其可否。门下先进。如吾先生者。乃严防如此。先生而如此。则馀人又可知。自此不敢复以广质同门。追补前说为念。只得私自存疑。更加反复。以觊其有启发耳。然于此心未释疑时。有人讨诘其所以不释疑之故。则不得不据实言之。以求闻针砭之论。如是不已。自然句语四出上下人辅颊。如下谕所设四者之虑。(正月十四日书中有此云云。)毕竟免不得。然亦莫可奈何矣。第念此心至公。此理至直。是为是非为非。守曰守改曰改。疑曰疑。只据眼中见成见识。且从面前直截路行将去。知之罪之。恭俟后之君子勘断之如何而已。馀外多般挂碍。恐不足深较。窃计先师当初立此论时。其处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4L 页
 心自应如此。今以此心为心。虽其议论枝叶。不能尽同。而本原大体。庶几不至甚相戾也。未知如何。
心自应如此。今以此心为心。虽其议论枝叶。不能尽同。而本原大体。庶几不至甚相戾也。未知如何。下谕言心是理气之合。鄙见政亦如此。盖惟理气之合也。故揔举全体则只唤做物。就其中指上一面。乃可以理言。且以尊说所引程子之言考之。所谓谷种非物之合理气者。而生之性。非指其中上一面者耶。至如心性对言。而以心为一而无对者。以当统体之太极。以性为两而有对者。以当各具之太极。(朱子言统体太极。各具太极。本就一原异体上立名。今以一性内有仁义礼智之分者为各具。以心之包含此性者为统体。面目终是不类。政使主心性分合。如先师之论。只此名目或非遗旨。恐合修改。)区区私见最所不安处。政在此一言。年前海上上书时。已发其端。其后反复愈久而愈不自得。要之竟此生。抱此耿耿耳。
上重庵先生(戊子二月十日)
先师文集。冬间谨依教指。考阅全部。其以气言心处。不为不多。而以心对性。作物则说处。无端的可指拟者。其所以然之故。似不出下书中所喻之意矣。惟因此一番熟读。益见其平生讲说主理大宗旨。悉本于养深积厚之中。而著为文词。光明磊落。尽有近世诸贤道不到处。弥不胜秋阳江汉之思矣。顾于其间精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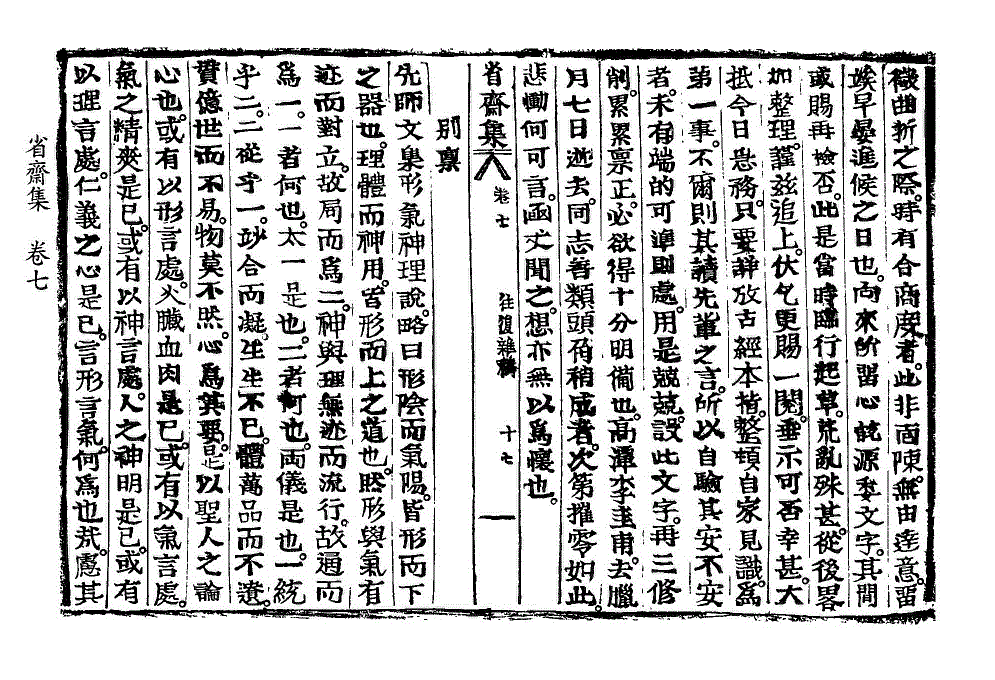 微曲折之际。时有合商度者。此非面陈。无由达意。留俟早晏进候之日也。向来所留心说源委文字。其间或赐再检否。此是当时临行起草。荒乱殊甚。从后略加整理。谨玆追上。伏乞更赐一阅。垂示可否幸甚。大抵今日急务。只要详考古经本指。整顿自家见识。为第一事。不尔则其读先辈之言。所以自验其安不安者。未有端的可准则处。用是兢兢。设此文字。再三修削。累累禀正。必欲得十分明备也。高潭李圭甫。去腊月七日逝去。同志善类头角稍成者。次第摧零如此。悲恸何可言。函丈闻之。想亦无以为怀也。
微曲折之际。时有合商度者。此非面陈。无由达意。留俟早晏进候之日也。向来所留心说源委文字。其间或赐再检否。此是当时临行起草。荒乱殊甚。从后略加整理。谨玆追上。伏乞更赐一阅。垂示可否幸甚。大抵今日急务。只要详考古经本指。整顿自家见识。为第一事。不尔则其读先辈之言。所以自验其安不安者。未有端的可准则处。用是兢兢。设此文字。再三修削。累累禀正。必欲得十分明备也。高潭李圭甫。去腊月七日逝去。同志善类头角稍成者。次第摧零如此。悲恸何可言。函丈闻之。想亦无以为怀也。别禀
先师文集形气神理说。略曰形阴而气阳。皆形而下之器也。理体而神用。皆形而上之道也。然形与气有迹而对立。故局而为二。神与理无迹而流行。故通而为一。一者何也。太一是也。二者何也。两仪是也。一统乎二。二从乎一。妙合而凝。生生不已。体万品而不遗。贯亿世而不易。物莫不然。心为其要。是以圣人之论心也。或有以形言处。火脏血肉是已。或有以气言处。气之精爽是已。或有以神言处。人之神明是已。或有以理言处。仁义之心是已。言形言气。何为也哉。虑其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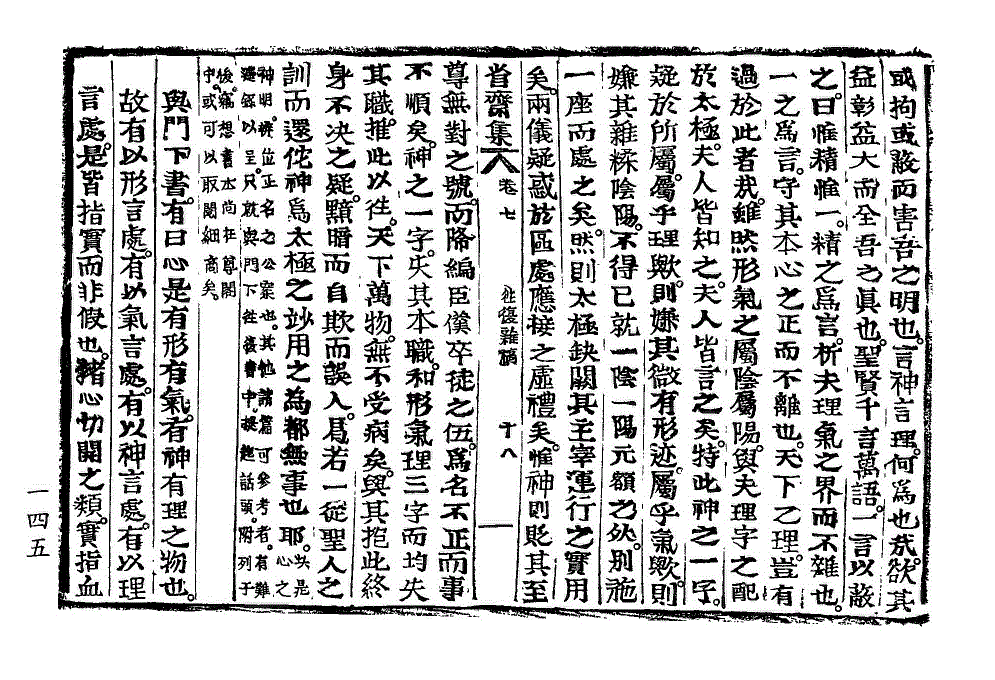 或拘或蔽而害吾之明也。言神言理。何为也哉。欲其益彰益大而全吾之真也。圣贤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惟精惟一。精之为言。析夫理气之界而不杂也。一之为言。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天下之理。岂有过于此者哉。虽然形气之属阴属阳。与夫理字之配于太极。夫人皆知之。夫人皆言之矣。特此神之一字。疑于所属。属乎理欤。则嫌其微有形迹。属乎气欤。则嫌其杂糅阴阳。不得已就一阴一阳元额之外。别施一座而处之矣。然则太极缺阙其主宰运行之实用矣。两仪疑惑于区处应接之虚礼矣。惟神则贬其至尊无对之号。而降编臣仆卒徒之伍。为名不正而事不顺矣。神之一字。失其本职。和形气理三字而均失其职。推此以往。天下万物。无不受病矣。与其抱此终身不决之疑。黯暗而自欺而误人。曷若一从圣人之训而还佗神为太极之妙用之为都无事也耶。(此是心之神明。辨位正名之公案也。其他诸篇可参考者。有难遍录以呈。只就与门下往复书中。提起话头。附列于后。窃想书本尚在尊阁中。或可以取阅细商矣。)
或拘或蔽而害吾之明也。言神言理。何为也哉。欲其益彰益大而全吾之真也。圣贤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惟精惟一。精之为言。析夫理气之界而不杂也。一之为言。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天下之理。岂有过于此者哉。虽然形气之属阴属阳。与夫理字之配于太极。夫人皆知之。夫人皆言之矣。特此神之一字。疑于所属。属乎理欤。则嫌其微有形迹。属乎气欤。则嫌其杂糅阴阳。不得已就一阴一阳元额之外。别施一座而处之矣。然则太极缺阙其主宰运行之实用矣。两仪疑惑于区处应接之虚礼矣。惟神则贬其至尊无对之号。而降编臣仆卒徒之伍。为名不正而事不顺矣。神之一字。失其本职。和形气理三字而均失其职。推此以往。天下万物。无不受病矣。与其抱此终身不决之疑。黯暗而自欺而误人。曷若一从圣人之训而还佗神为太极之妙用之为都无事也耶。(此是心之神明。辨位正名之公案也。其他诸篇可参考者。有难遍录以呈。只就与门下往复书中。提起话头。附列于后。窃想书本尚在尊阁中。或可以取阅细商矣。)与门下书。有曰心是有形有气。有神有理之物也。故有以形言处。有以气言处。有以神言处。有以理言处。是皆指实而非假也。猪心切开之类。实指血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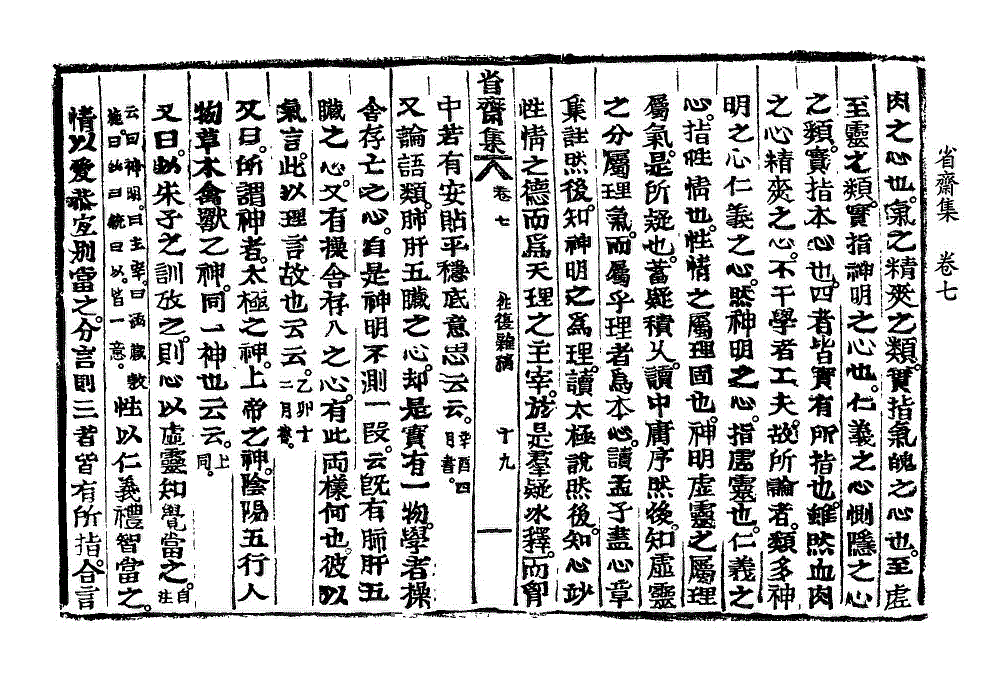 肉之心也。气之精爽之类。实指气魄之心也。至虚至灵之类。实指神明之心也。仁义之心恻隐之心之类。实指本心也。四者皆实有所指也。虽然血肉之心精爽之心。不干学者工夫。故所论者。类多神明之心仁义之心。然神明之心。指虚灵也。仁义之心。指性情也。性情之属理固也。神明虚灵之属理属气。是所疑也。蓄疑积久。读中庸序然后。知虚灵之分属理气。而属乎理者为本心。读孟子尽心章集注然后。知神明之为理。读太极说然后。知心妙性情之德而为天理之主宰。于是群疑冰释。而胸中若有安贴平稳底意思云云。(辛酉四月书。)
肉之心也。气之精爽之类。实指气魄之心也。至虚至灵之类。实指神明之心也。仁义之心恻隐之心之类。实指本心也。四者皆实有所指也。虽然血肉之心精爽之心。不干学者工夫。故所论者。类多神明之心仁义之心。然神明之心。指虚灵也。仁义之心。指性情也。性情之属理固也。神明虚灵之属理属气。是所疑也。蓄疑积久。读中庸序然后。知虚灵之分属理气。而属乎理者为本心。读孟子尽心章集注然后。知神明之为理。读太极说然后。知心妙性情之德而为天理之主宰。于是群疑冰释。而胸中若有安贴平稳底意思云云。(辛酉四月书。)又论语类。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学者操舍存亡之心。自是神明不测一段。云既有肺肝五脏之心。又有操舍存入之心。有此两样何也。彼以气言。此以理言故也云云。(乙卯十二月书。)
又曰。所谓神者。太极之神。上帝之神。阴阳五行人物草木禽兽之神。同一神也云云。(上同。)
又曰。以朱子之训考之。则心以虚灵知觉当之。(自注云曰神明。曰主宰。曰涵藏敷施。曰妙曰统曰以。皆一意。)性以仁义礼智当之。情以爱恭宜别当之。分言则三者皆有所指。合言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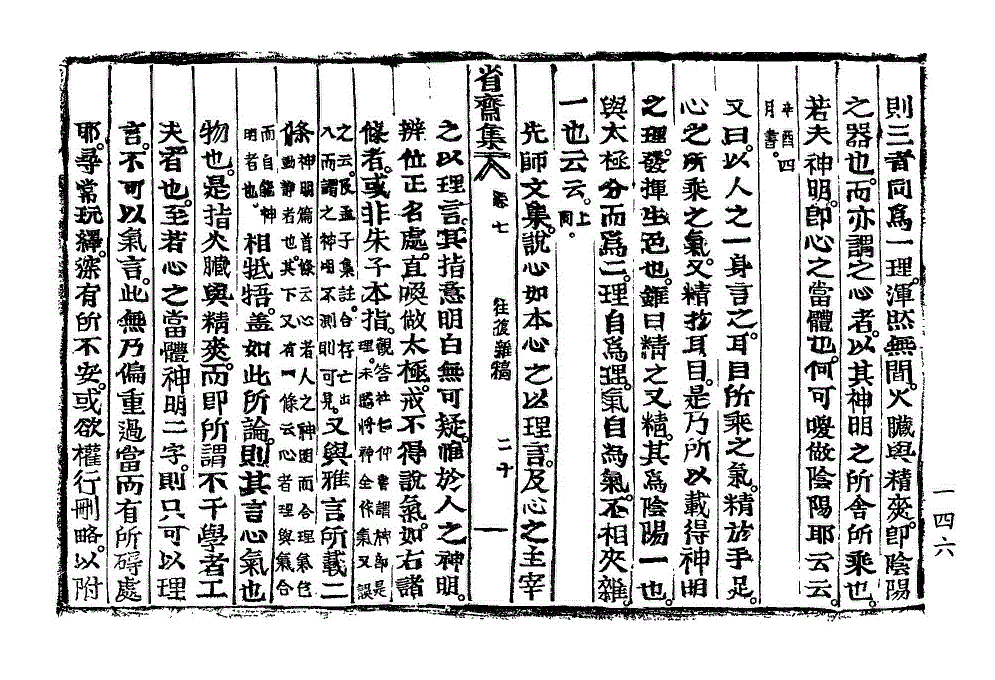 则三者同为一理。浑然无间。火脏与精爽。即阴阳之器也。而亦谓之心者。以其神明之所舍所乘也。若夫神明。即心之当体也。何可唤做阴阳耶云云。(辛酉四月书。)
则三者同为一理。浑然无间。火脏与精爽。即阴阳之器也。而亦谓之心者。以其神明之所舍所乘也。若夫神明。即心之当体也。何可唤做阴阳耶云云。(辛酉四月书。)又曰。以人之一身言之。耳目所乘之气。精于手足。心之所乘之气。又精于耳目。是乃所以载得神明之理。发挥生色也。虽曰精之又精。其为阴阳一也。与太极分而为二。理自为理。气自为气。不相夹杂。一也云云。(上同。)
先师文集。说心如本心之以理言。及心之主宰之以理言。其指意明白无可疑。惟于人之神明。辨位正名处。直唤做太极。戒不得说气。如右诸条者。或非朱子本指。(观答杜仁仲书谓神即是理未然。将神全作气又误之云。及孟子集注。合存亡出入而谓之神明不测则可见。)又与雅言所载二条(神明篇首条云心者人之神明而合理气包动静者也。其下又有一条云心者理与气合而自能神明者也。)相牴牾。盖如此所论。则其言心气也物也。是指火脏与精爽。而即所谓不干学者工夫者也。至若心之当体神明二字。则只可以理言。不可以气言。此无乃偏重过当而有所碍处耶。寻常玩绎。深有所不安。或欲权行删略。以附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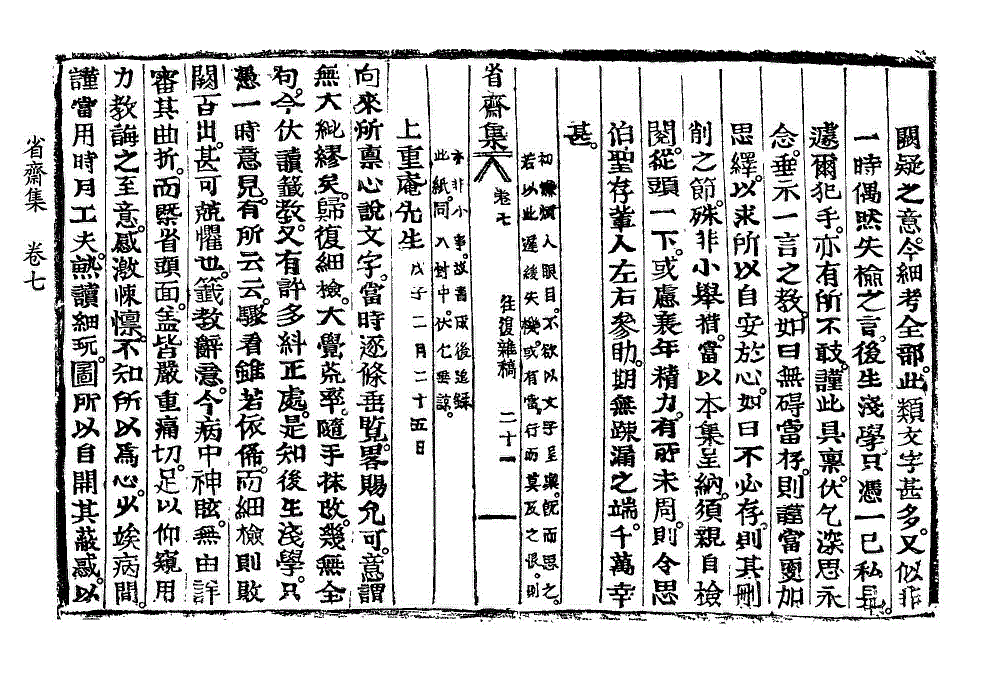 阙疑之意。今细考全部。此类文字甚多。又似非一时偶然失检之言。后生浅学。只凭一己私见。遽尔犯手。亦有所不敢。谨此具禀。伏乞深思永念。垂示一言之教。如曰无碍当存。则谨当更加思绎。以求所以自安于心。如曰不必存。则其删削之节。殊非小举措。当以本集呈纳。须亲自检阅。从头一下。或虑衰年精力。有所未周。则令思伯圣存辈人左右参助。期无疏漏之端。千万幸甚。
阙疑之意。今细考全部。此类文字甚多。又似非一时偶然失检之言。后生浅学。只凭一己私见。遽尔犯手。亦有所不敢。谨此具禀。伏乞深思永念。垂示一言之教。如曰无碍当存。则谨当更加思绎。以求所以自安于心。如曰不必存。则其删削之节。殊非小举措。当以本集呈纳。须亲自检阅。从头一下。或虑衰年精力。有所未周。则令思伯圣存辈人左右参助。期无疏漏之端。千万幸甚。(初嫌烦人眼目。不欲以文字呈禀。既而思之。若以此迟缓失机。或有当行而莫及之恨。则亦非小事。故书成后追录此纸。同入封中。伏乞垂谅。)
上重庵先生(戊子二月二十五日)
向来所禀心说文字。当时逐条垂览。略赐允可。意谓无大纰缪矣。归复细检。大觉荒率。随手抹改。几无全句。今伏读签教。又有许多纠正处。是知后生浅学。只凭一时意见。有所云云。骤看虽若依俙。而细检则败阙百出。甚可兢惧也。签教辞意。今病中神眩。无由详审其曲折。而槩省头面。盖皆严重痛切。足以仰窥用力教诲之至意。感激悚懔。不知所以为心。少俟病间。谨当用时月工夫。熟读细玩。图所以自开其蔽惑。以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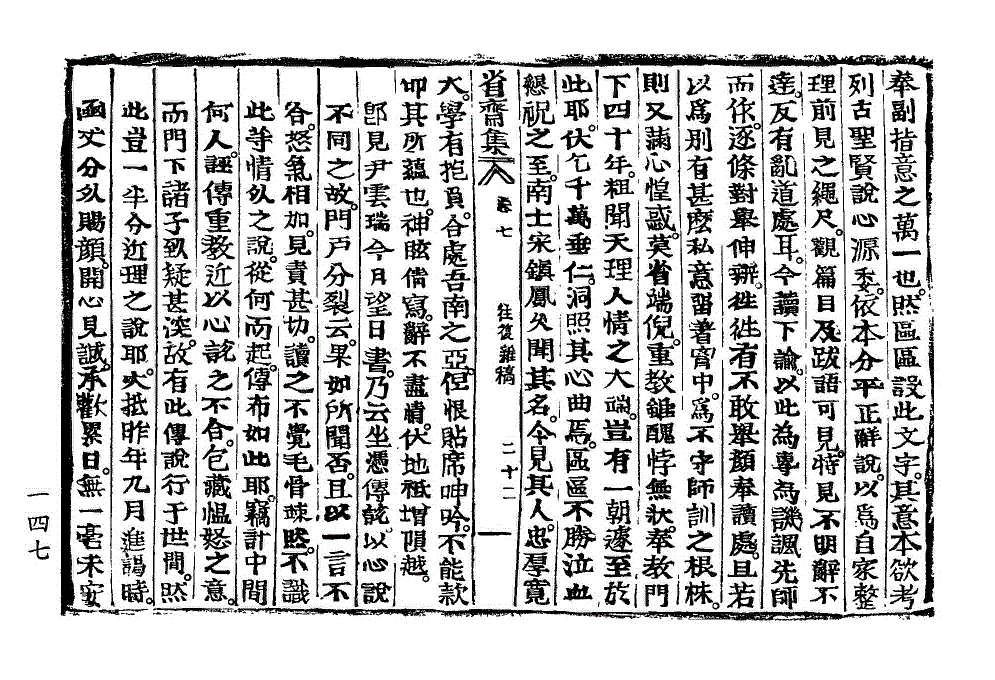 奉副指意之万一也。然区区设此文字。其意本欲考列古圣贤说心源委。依本分平正解说。以为自家整理前见之绳尺。观篇目及跋语可见。特见不明辞不达。反有乱道处耳。今读下谕。以此为专为讥讽先师而作。逐条对举伸辨。往往有不敢举颜奉读处。且若以为别有甚么私意留着胸中。为不守师训之根株。则又满心惶惑。莫省端倪。重教虽丑悖无状。奉教门下四十年。粗闻天理人情之大端。岂有一朝遽至于此耶。伏乞千万垂仁。洞照其心曲焉。区区不胜泣血恳祝之至。南士宋镇凤久闻其名。今见其人。忠厚宽大。学有抱负。合处吾南之亚。但恨贴席呻吟。不能款叩其所蕴也。神眩倩写。辞不尽情。伏地祗增陨越。
奉副指意之万一也。然区区设此文字。其意本欲考列古圣贤说心源委。依本分平正解说。以为自家整理前见之绳尺。观篇目及跋语可见。特见不明辞不达。反有乱道处耳。今读下谕。以此为专为讥讽先师而作。逐条对举伸辨。往往有不敢举颜奉读处。且若以为别有甚么私意留着胸中。为不守师训之根株。则又满心惶惑。莫省端倪。重教虽丑悖无状。奉教门下四十年。粗闻天理人情之大端。岂有一朝遽至于此耶。伏乞千万垂仁。洞照其心曲焉。区区不胜泣血恳祝之至。南士宋镇凤久闻其名。今见其人。忠厚宽大。学有抱负。合处吾南之亚。但恨贴席呻吟。不能款叩其所蕴也。神眩倩写。辞不尽情。伏地祗增陨越。即见尹云瑞今月望日书。乃云坐凭传说。以心说不同之故。门户分裂云。果如所闻否。且以一言不合。怒气相加。见责甚切。读之不觉毛骨竦然。不识此等情外之说。从何而起。传布如此耶。窃计中间何人。诬传重教近以心说之不合。包藏愠怒之意。而门下诸子致疑甚深。故有此传说行于世间。然此岂一半分近理之说耶。大抵昨年九月进谒时。函丈分外赐颜。开心见诚。承观累日。无一毫未安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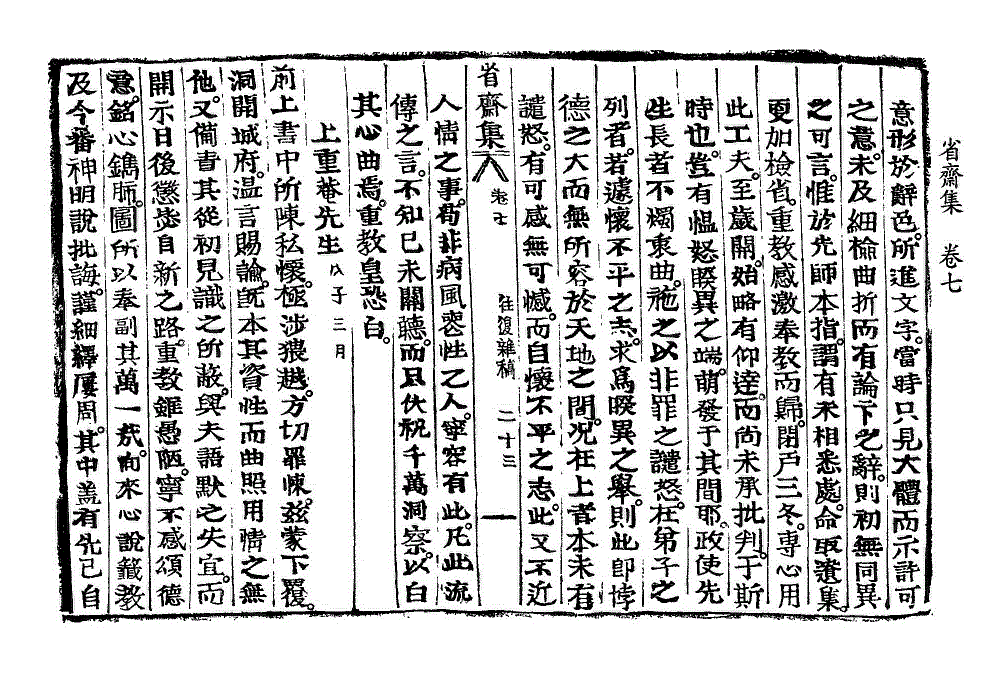 意形于辞色。所进文字。当时只见大体而示许可之意。未及细检曲折而有论卞之辞。则初无同异之可言。惟于先师本指。谓有未相悉处。命取遗集。更加检省。重教感激奉教而归。闭户三冬。专心用此工夫。至岁开。始略有仰达。而尚未承批判。于斯时也。岂有愠怒睽异之端。萌发于其间耶。政使先生长者不烛衷曲。施之以非罪之谴怒。在弟子之列者。若遽怀不平之志。求为睽异之举。则此即悖德之大而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况在上者本未有谴怒。有可感无可憾。而自怀不平之志。此又不近人情之事。苟非病风丧性之人。宁容有此。凡此流传之言。不知已未关听。而只伏祝千万洞察。以白其心曲焉。重教皇恐白。
意形于辞色。所进文字。当时只见大体而示许可之意。未及细检曲折而有论卞之辞。则初无同异之可言。惟于先师本指。谓有未相悉处。命取遗集。更加检省。重教感激奉教而归。闭户三冬。专心用此工夫。至岁开。始略有仰达。而尚未承批判。于斯时也。岂有愠怒睽异之端。萌发于其间耶。政使先生长者不烛衷曲。施之以非罪之谴怒。在弟子之列者。若遽怀不平之志。求为睽异之举。则此即悖德之大而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况在上者本未有谴怒。有可感无可憾。而自怀不平之志。此又不近人情之事。苟非病风丧性之人。宁容有此。凡此流传之言。不知已未关听。而只伏祝千万洞察。以白其心曲焉。重教皇恐白。上重庵先生(戊子三月)
前上书中所陈私怀。极涉猥越。方切罪悚。玆蒙下覆。洞开城府。温言赐谕。既本其资性而曲照用情之无他。又备责其从初见识之所蔽。与夫语默之失宜。而开示日后惩毖自新之路。重教虽愚陋。宁不感颂德意。铭心镌肺。图所以奉副其万一哉。向来心说签教及今番神明说批诲。谨细绎屡周。其中盖有先已自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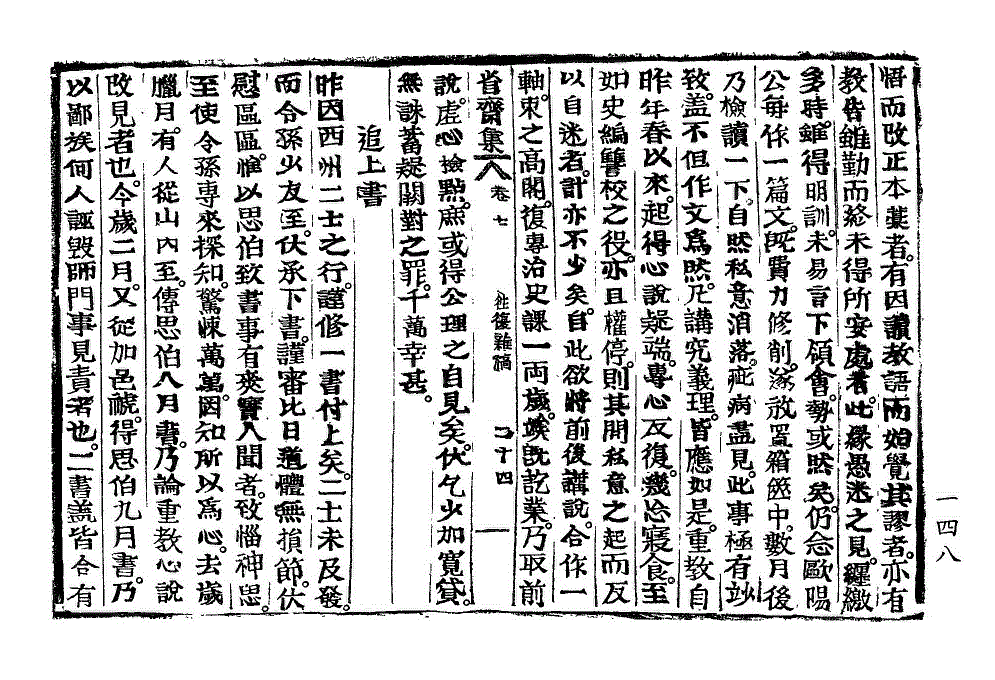 悟而改正本藁者。有因读教语而始觉其谬者。亦有教告虽勤而终未得所安处者。此缘愚迷之见。缠缴多时。虽得明训。未易言下领会。势或然矣。仍念欧阳公每作一篇文。既费力修削。遂放置箱箧中。数月后乃检读一下。自然私意消落。疵病尽见。此事极有妙致。盖不但作文为然。凡讲究义理。皆应如是。重教自昨年春以来。起得心说疑端。专心反复。几忘寝食。至如史编雠校之役。亦且权停。则其间私意之起而反以自迷者。计亦不少矣。自此欲将前后讲说。合作一轴。束之高阁。复专治史课一两岁。俟既讫业。乃取前说。虚心检点。庶或得公理之自见矣。伏乞少加宽贷。无诛蓄疑阙对之罪。千万幸甚。
悟而改正本藁者。有因读教语而始觉其谬者。亦有教告虽勤而终未得所安处者。此缘愚迷之见。缠缴多时。虽得明训。未易言下领会。势或然矣。仍念欧阳公每作一篇文。既费力修削。遂放置箱箧中。数月后乃检读一下。自然私意消落。疵病尽见。此事极有妙致。盖不但作文为然。凡讲究义理。皆应如是。重教自昨年春以来。起得心说疑端。专心反复。几忘寝食。至如史编雠校之役。亦且权停。则其间私意之起而反以自迷者。计亦不少矣。自此欲将前后讲说。合作一轴。束之高阁。复专治史课一两岁。俟既讫业。乃取前说。虚心检点。庶或得公理之自见矣。伏乞少加宽贷。无诛蓄疑阙对之罪。千万幸甚。追上书
昨因西州二士之行。谨修一书付上矣。二士未及发。而令孙少友至。伏承下书。谨审比日道体无损节。伏慰区区。惟以思伯致书事有爽实入闻者。致恼神思。至使令孙专来探知。惊悚万万。罔知所以为心。去岁腊月。有人从山内至。传思伯八月书。乃论重教心说改见者也。今岁二月。又从加邑褫。得思伯九月书。乃以鄙族何人诬毁师门事见责者也。二书盖皆合有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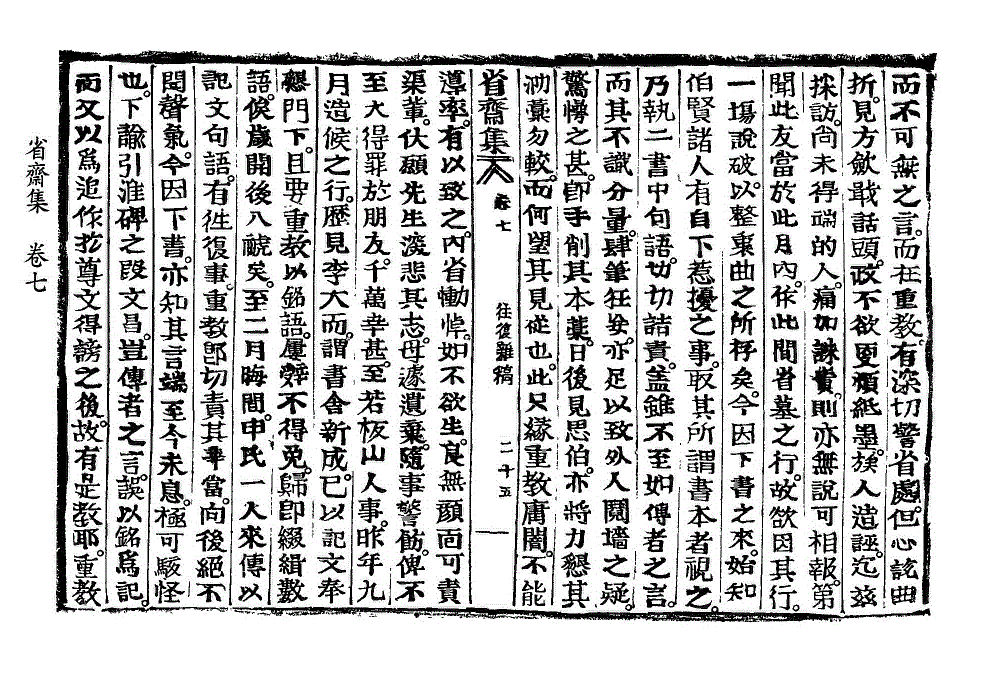 而不可无之言。而在重教。有深切警省处。但心说曲折。见方敛戢话头。政不欲更烦纸墨。族人造诬。迄玆采访。尚未得端的人。痛加诛责。则亦无说可相报。第闻此友当于此月内。作此间省墓之行。故欲因其行。一场说破。以整衷曲之所存矣。今因下书之来。始知伯贤诸人有自下惹扰之事。取其所谓书本者视之。乃执二书中句语。切切诘责。盖虽不至如传者之言。而其不识分量。肆笔狂妄。亦足以致外人阋墙之疑。惊愕之甚。即手削其本藁。日后见思伯。亦将力恳其泐藁勿较。而何望其见从也。此只缘重教庸闇。不能导率。有以致之。内省恸悼。如不欲生。良无颜面可责渠辈。伏愿先生深悲其志。毋遽遗弃。随事警饬。俾不至大得罪于朋友。千万幸甚。至若板山人事。昨年九月造候之行。历见李大而。谓书舍新成。已以记文奉恳门下。且要重教以铭语。屡辞不得免。归即缀缉数语。俟岁开后入褫矣。至二月晦间。申氏一人来传以记文句语。有往复事。重教即切责其乖当。向后绝不闻声气。今因下书。亦知其言端至今未息。极可骇怪也。下谕引淮碑之段文昌。岂传者之言。误以铭为记。而又以为追作于尊文得谤之后。故有是教耶。重教
而不可无之言。而在重教。有深切警省处。但心说曲折。见方敛戢话头。政不欲更烦纸墨。族人造诬。迄玆采访。尚未得端的人。痛加诛责。则亦无说可相报。第闻此友当于此月内。作此间省墓之行。故欲因其行。一场说破。以整衷曲之所存矣。今因下书之来。始知伯贤诸人有自下惹扰之事。取其所谓书本者视之。乃执二书中句语。切切诘责。盖虽不至如传者之言。而其不识分量。肆笔狂妄。亦足以致外人阋墙之疑。惊愕之甚。即手削其本藁。日后见思伯。亦将力恳其泐藁勿较。而何望其见从也。此只缘重教庸闇。不能导率。有以致之。内省恸悼。如不欲生。良无颜面可责渠辈。伏愿先生深悲其志。毋遽遗弃。随事警饬。俾不至大得罪于朋友。千万幸甚。至若板山人事。昨年九月造候之行。历见李大而。谓书舍新成。已以记文奉恳门下。且要重教以铭语。屡辞不得免。归即缀缉数语。俟岁开后入褫矣。至二月晦间。申氏一人来传以记文句语。有往复事。重教即切责其乖当。向后绝不闻声气。今因下书。亦知其言端至今未息。极可骇怪也。下谕引淮碑之段文昌。岂传者之言。误以铭为记。而又以为追作于尊文得谤之后。故有是教耶。重教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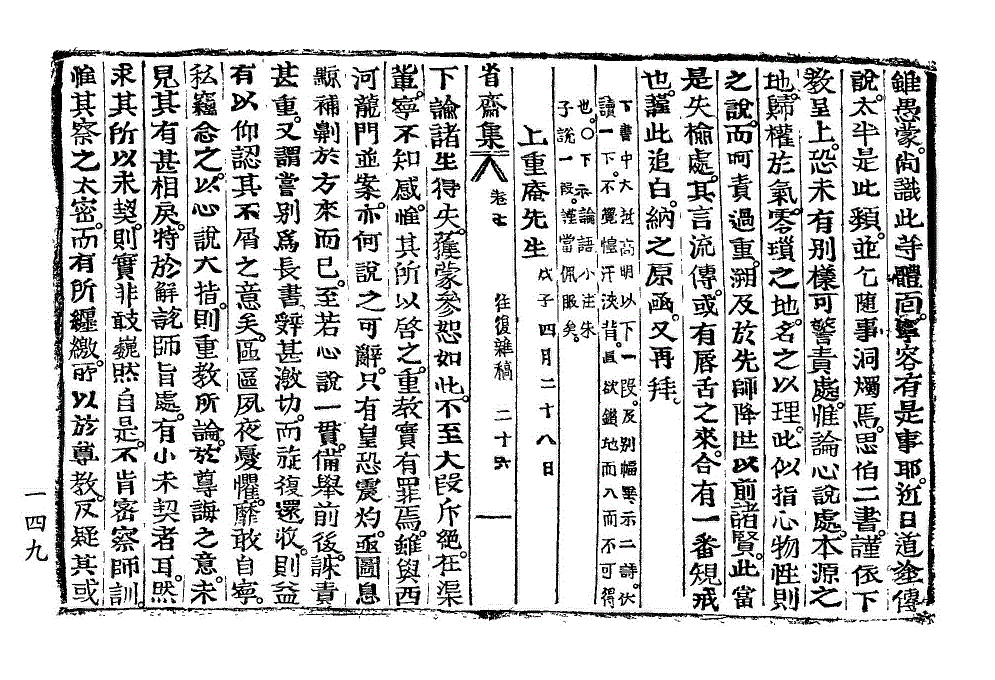 虽愚蒙。尚识此等体面。宁容有是事耶。近日道涂传说。太半是此类。并乞随事洞烛焉。思伯二书。谨依下教呈上。恐未有别样可警责处。惟论心说处。本源之地。归权于气。零琐之地。名之以理。此似指心物性则之说。而呵责过重。溯及于先师降世以前诸贤。此当是失检处。其言流传。或有唇舌之来。合有一番规戒也。谨此追白。纳之原函。又再拜。
虽愚蒙。尚识此等体面。宁容有是事耶。近日道涂传说。太半是此类。并乞随事洞烛焉。思伯二书。谨依下教呈上。恐未有别样可警责处。惟论心说处。本源之地。归权于气。零琐之地。名之以理。此似指心物性则之说。而呵责过重。溯及于先师降世以前诸贤。此当是失检处。其言流传。或有唇舌之来。合有一番规戒也。谨此追白。纳之原函。又再拜。(下书中大抵高明以下一段。及别幅垂示二诗。伏读一下。不觉惶汗浃背。直欲钻地而入而不可得也。○下示论语小注朱子说一段。谨当佩服矣。)
上重庵先生(戊子四月二十八日)
下谕诸生得失。获蒙参恕如此。不至大段斥绝。在渠辈。宁不知感。惟其所以启之。重教实有罪焉。虽与西河龙门并案。亦何说之可辞。只有皇恐震灼。亟图息黥补劓于方来而已。至若心说一贯。备举前后。诛责甚重。又谓尝别为长书。辞甚激切。而旋复还收。则益有以仰认其不屑之意矣。区区夙夜忧惧。靡敢自宁。私窃念之。以心说大指。则重教所论。于尊诲之意。未见其有甚相戾。特于解说师旨处。有小未契者耳。然求其所以未契。则实非敢巍然自是。不肯密察师训。惟其察之太密。而有所缠缴。所以于尊教。反疑其或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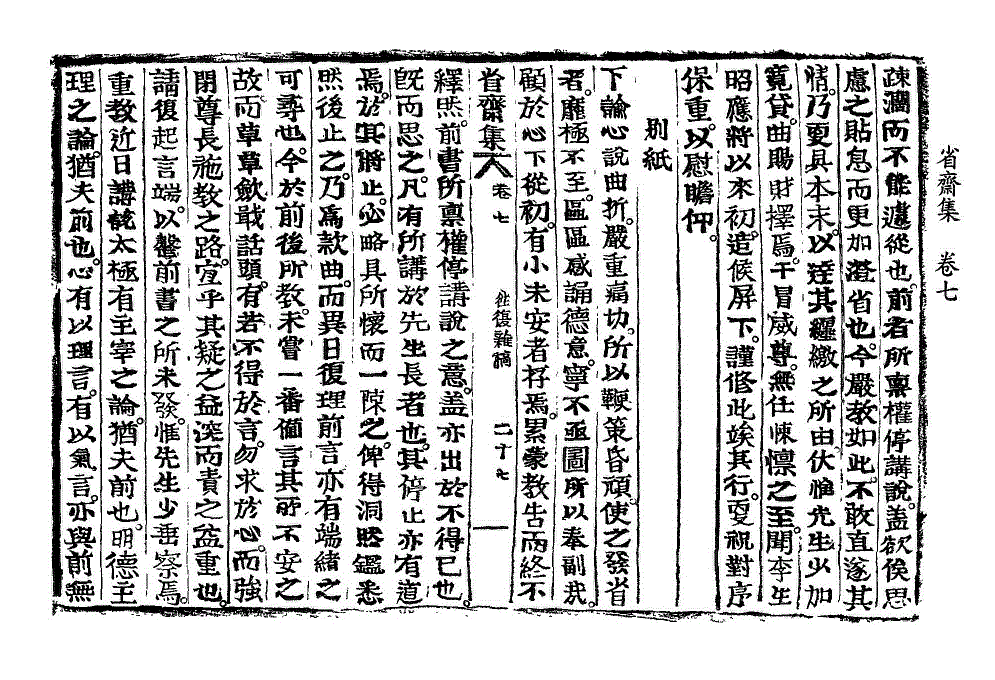 疏阔而不能遽从也。前者所禀权停讲说。盖欲俟思虑之贴息而更加澄省也。今严教如此。不敢直遂其情。乃更具本末。以达其缠缴之所由。伏惟先生少加宽贷。曲赐财择焉。干冒威尊。无任悚懔之至。闻李生昭应将以来初。造候屏下。谨修此俟其行。更祝对序保重。以慰瞻仰。
疏阔而不能遽从也。前者所禀权停讲说。盖欲俟思虑之贴息而更加澄省也。今严教如此。不敢直遂其情。乃更具本末。以达其缠缴之所由。伏惟先生少加宽贷。曲赐财择焉。干冒威尊。无任悚懔之至。闻李生昭应将以来初。造候屏下。谨修此俟其行。更祝对序保重。以慰瞻仰。别纸
下谕心说曲折。严重痛切。所以鞭策昏顽。使之发省者。靡极不至。区区感诵德意。宁不亟图所以奉副哉。顾于心下从初。有小未安者存焉。累蒙教告而终不释然。前书所禀权停讲说之意。盖亦出于不得已也。既而思之。凡有所讲于先生长者也。其停止亦有道焉。于其将止。必略具所怀而一陈之。俾得洞然鉴悉然后止之。乃为款曲。而异日复理前言亦有端绪之可寻也。今于前后所教。未尝一番备言其所不安之故。而草草敛戢话头。有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强闭尊长施教之路。宜乎其疑之益深而责之益重也。请复起言端。以罄前书之所未发。惟先生少垂察焉。重教近日讲说太极有主宰之论。犹夫前也。明德主理之论。犹夫前也。心有以理言。有以气言。亦与前无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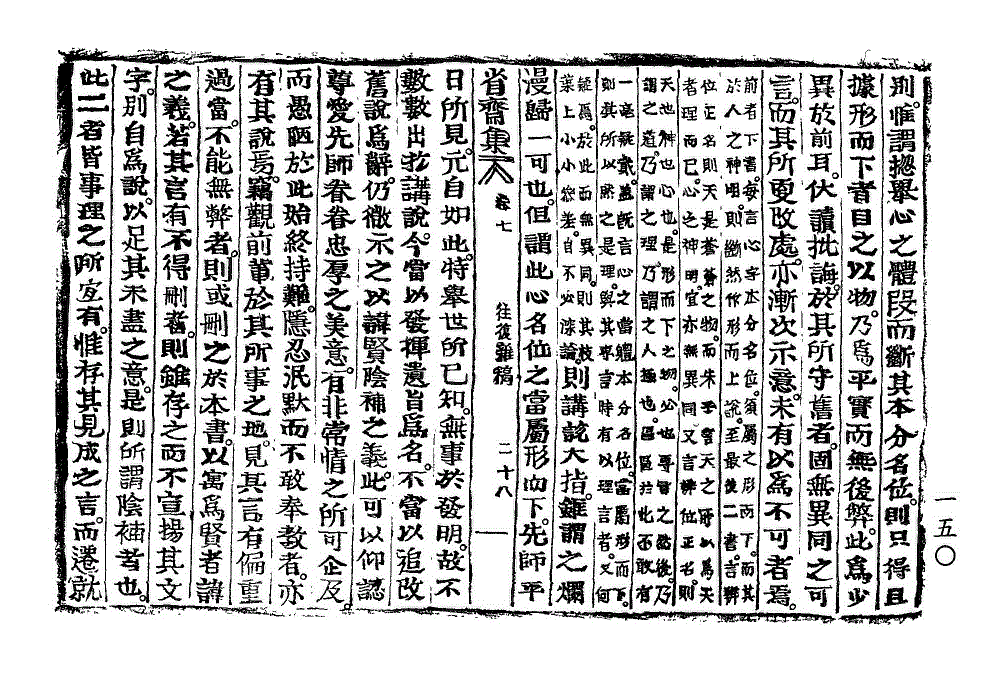 别。惟谓揔举心之体段而断其本分名位。则只得且据形而下者目之以物。乃为平实而无后弊。此为少异于前耳。伏读批诲。于其所守旧者。固无异同之可言。而其所更改处。亦渐次示意。未有以为不可者焉。(前者下书。每言心字本分名位。须属之形而下。而其于人之神明。则断然作形而上说。至最后二书。言辨位正名则天是苍苍之物。而朱子言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心之神明。宜亦无异同。又言辨位正名。则天也神也心也。是形而下之物。必也专言之然后。乃谓之道。乃谓之理。乃谓之人极也。区区于此不敢有一毫疑贰。盖既言心之当体本分名位。当属形而下。则其所以然之是理。与其专言时有以理言者。又何疑焉。于此而无异同。则其枝叶上小小参差。自不必深论。)则讲说大指。虽谓之烂漫归一可也。但谓此心名位之当属形而下。先师平日所见。元自如此。特举世所已知。无事于发明。故不数数出于讲说。今当以发挥遗旨为名。不当以追改旧说为辞。仍微示之以讳贤阴补之义。此可以仰认尊爱先师眷眷忠厚之美意。有非常情之所可企及。而愚陋于此始终持难。隐忍泯默而不敢奉教者。亦有其说焉。窃观前辈于其所事之地。见其言有偏重过当。不能无㢢者。则或删之于本书。以寓为贤者讳之义。若其言有不得删者。则虽存之而不宣扬其文字。别自为说。以足其未尽之意。是则所谓阴补者也。此二者皆事理之所宜有。惟存其见成之言。而迁就
别。惟谓揔举心之体段而断其本分名位。则只得且据形而下者目之以物。乃为平实而无后弊。此为少异于前耳。伏读批诲。于其所守旧者。固无异同之可言。而其所更改处。亦渐次示意。未有以为不可者焉。(前者下书。每言心字本分名位。须属之形而下。而其于人之神明。则断然作形而上说。至最后二书。言辨位正名则天是苍苍之物。而朱子言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心之神明。宜亦无异同。又言辨位正名。则天也神也心也。是形而下之物。必也专言之然后。乃谓之道。乃谓之理。乃谓之人极也。区区于此不敢有一毫疑贰。盖既言心之当体本分名位。当属形而下。则其所以然之是理。与其专言时有以理言者。又何疑焉。于此而无异同。则其枝叶上小小参差。自不必深论。)则讲说大指。虽谓之烂漫归一可也。但谓此心名位之当属形而下。先师平日所见。元自如此。特举世所已知。无事于发明。故不数数出于讲说。今当以发挥遗旨为名。不当以追改旧说为辞。仍微示之以讳贤阴补之义。此可以仰认尊爱先师眷眷忠厚之美意。有非常情之所可企及。而愚陋于此始终持难。隐忍泯默而不敢奉教者。亦有其说焉。窃观前辈于其所事之地。见其言有偏重过当。不能无㢢者。则或删之于本书。以寓为贤者讳之义。若其言有不得删者。则虽存之而不宣扬其文字。别自为说。以足其未尽之意。是则所谓阴补者也。此二者皆事理之所宜有。惟存其见成之言。而迁就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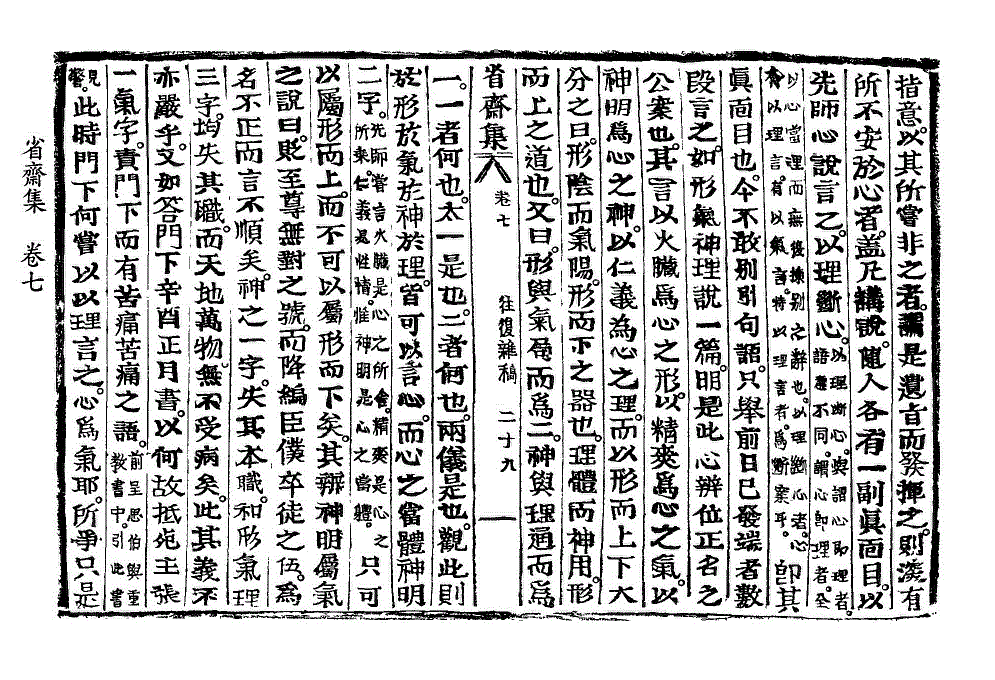 指意。以其所尝非之者。谓是遗旨而发挥之。则深有所不安于心者。盖凡讲说。随人各有一副真面目。以先师心说言之。以理断心。(以理断心。与谓心即理者。语意不同。谓心即理者。全以心当理而无复拣别之辞也。以理断心者。心有以理言。有以气言。特以理言者。为断案耳。)即其真面目也。今不敢别引句语。只举前日已发端者数段言之。如形气神理说一篇。明是此心辨位正名之公案也。其言以火脏为心之形。以精爽为心之气。以神明为心之神。以仁义为心之理。而以形而上下大分之曰。形阴而气阳。形而下之器也。理体而神用。形而上之道也。又曰。形与气局而为二。神与理通而为一。一者何也。太一是也。二者何也。两仪是也。观此则于形于气于神于理。皆可以言心。而心之当体神明二字。(先师尝言火脏是心之所舍。精爽是心之所乘。仁义是性情。惟神明是心之当体。)只可以属形而上。而不可以属形而下矣。其辨神明属气之说曰。贬至尊无对之号。而降编臣仆卒徒之伍。为名不正而言不顺矣。神之一字。失其本职。和形气理三字。均失其职。而天地万物。无不受病矣。此其义不亦严乎。又如答门下辛酉正月书。以何故抵死主张一气字。责门下而有苦痛苦痛之语。(前呈思伯与重教书中。引此书见警。)此时门下何尝以以理言之心为气耶。所争只是
指意。以其所尝非之者。谓是遗旨而发挥之。则深有所不安于心者。盖凡讲说。随人各有一副真面目。以先师心说言之。以理断心。(以理断心。与谓心即理者。语意不同。谓心即理者。全以心当理而无复拣别之辞也。以理断心者。心有以理言。有以气言。特以理言者。为断案耳。)即其真面目也。今不敢别引句语。只举前日已发端者数段言之。如形气神理说一篇。明是此心辨位正名之公案也。其言以火脏为心之形。以精爽为心之气。以神明为心之神。以仁义为心之理。而以形而上下大分之曰。形阴而气阳。形而下之器也。理体而神用。形而上之道也。又曰。形与气局而为二。神与理通而为一。一者何也。太一是也。二者何也。两仪是也。观此则于形于气于神于理。皆可以言心。而心之当体神明二字。(先师尝言火脏是心之所舍。精爽是心之所乘。仁义是性情。惟神明是心之当体。)只可以属形而上。而不可以属形而下矣。其辨神明属气之说曰。贬至尊无对之号。而降编臣仆卒徒之伍。为名不正而言不顺矣。神之一字。失其本职。和形气理三字。均失其职。而天地万物。无不受病矣。此其义不亦严乎。又如答门下辛酉正月书。以何故抵死主张一气字。责门下而有苦痛苦痛之语。(前呈思伯与重教书中。引此书见警。)此时门下何尝以以理言之心为气耶。所争只是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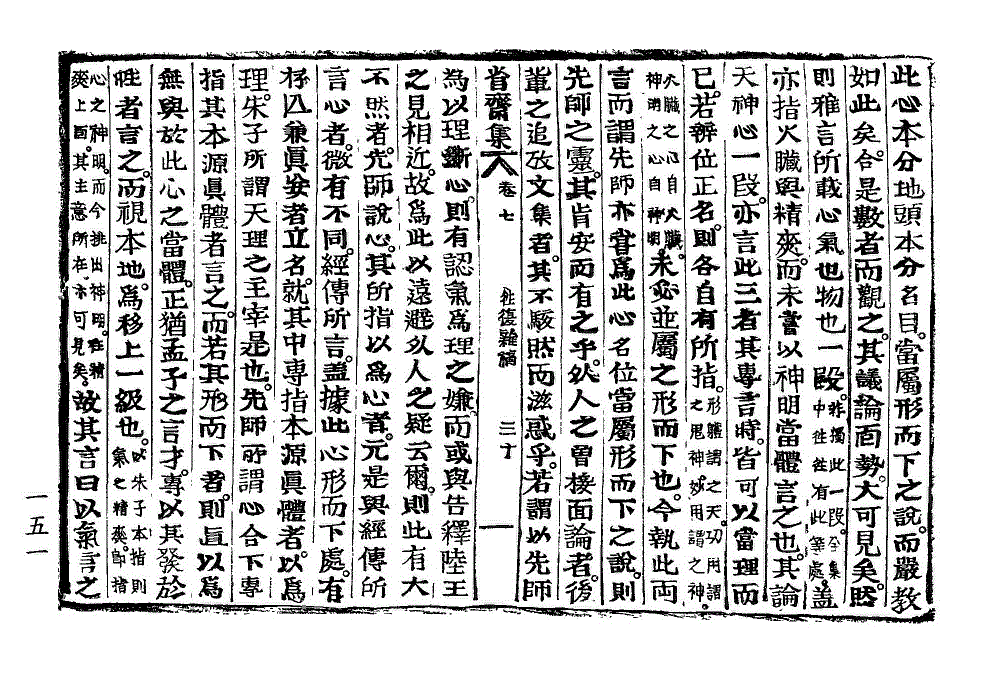 此心本分地头本分名目。当属形而下之说。而严教如此矣。合是数者而观之。其议论面势。大可见矣。然则雅言所载心气也物也一段。(非独此一段。全集中往往有此等处。)盖亦指火脏与精爽。而未尝以神明当体言之也。其论天神心一段。亦言此三者其专言时。皆可以当理而已。若辨位正名。则各自有所指。(形体谓之天。功用谓之鬼神。妙用谓之神。火脏之心自火脏。神明之心自神明。)未必并属之形而下也。今执此两言而谓先师亦尝为此心名位当属形而下之说。则先师之灵。其肯安而有之乎。外人之曾接面论者。后辈之追考文集者。其不骇然而滋惑乎。若谓以先师为以理断心。则有认气为理之嫌。而或与告释陆王之见相近。故为此以远避外人之疑云尔。则此有大不然者。先师说心。其所指以为心者。元是与经传所言心者。微有不同。经传所言。盖据此心形而下处。有存亡兼真妄者立名。就其中专指本源真体者。以为理。朱子所谓天理之主宰是也。先师所谓心合下专指其本源真体者言之。而若其形而下者。则直以为无与于此心之当体。正犹孟子之言才。专以其发于性者言之。而视本地。为移上一级也。(以朱子本指则气之精爽。即指心之神明。而今挑出神明。在精爽上面。其主意所在。亦可见矣。)故其言曰以气言之
此心本分地头本分名目。当属形而下之说。而严教如此矣。合是数者而观之。其议论面势。大可见矣。然则雅言所载心气也物也一段。(非独此一段。全集中往往有此等处。)盖亦指火脏与精爽。而未尝以神明当体言之也。其论天神心一段。亦言此三者其专言时。皆可以当理而已。若辨位正名。则各自有所指。(形体谓之天。功用谓之鬼神。妙用谓之神。火脏之心自火脏。神明之心自神明。)未必并属之形而下也。今执此两言而谓先师亦尝为此心名位当属形而下之说。则先师之灵。其肯安而有之乎。外人之曾接面论者。后辈之追考文集者。其不骇然而滋惑乎。若谓以先师为以理断心。则有认气为理之嫌。而或与告释陆王之见相近。故为此以远避外人之疑云尔。则此有大不然者。先师说心。其所指以为心者。元是与经传所言心者。微有不同。经传所言。盖据此心形而下处。有存亡兼真妄者立名。就其中专指本源真体者。以为理。朱子所谓天理之主宰是也。先师所谓心合下专指其本源真体者言之。而若其形而下者。则直以为无与于此心之当体。正犹孟子之言才。专以其发于性者言之。而视本地。为移上一级也。(以朱子本指则气之精爽。即指心之神明。而今挑出神明。在精爽上面。其主意所在。亦可见矣。)故其言曰以气言之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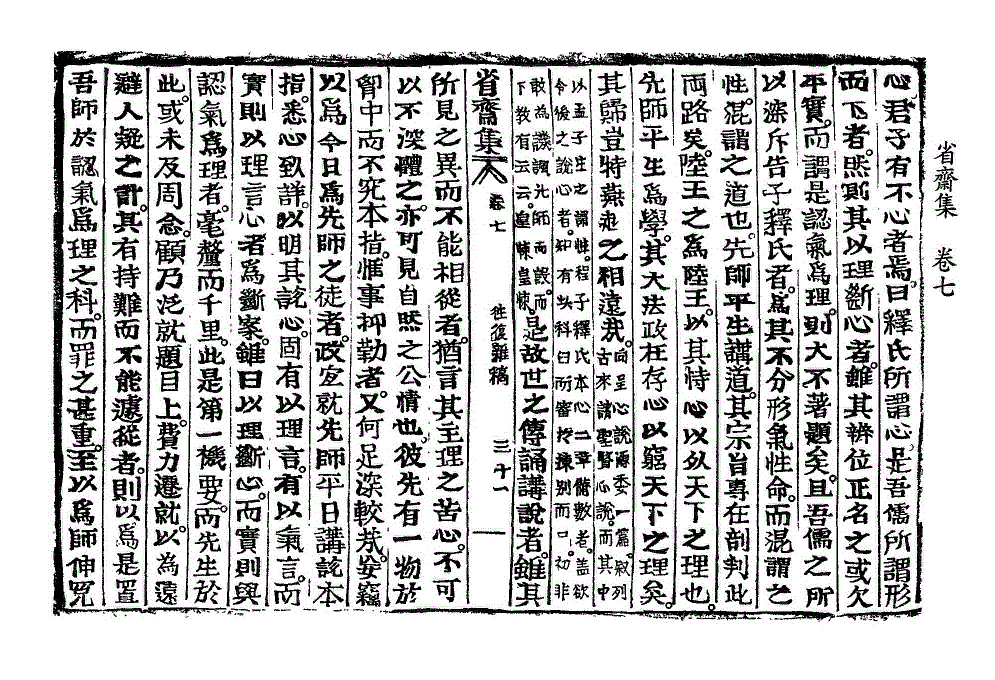 心。君子有不心者焉。曰释氏所谓心。是吾儒所谓形而下者。然则其以理断心者。虽其辨位正名之或欠平实。而谓是认气为理。则大不著题矣。且吾儒之所以深斥告子释氏者。为其不分形气性命。而混谓之性。混谓之道也。先师平生讲道。其宗旨专在剖判此两路矣。陆王之为陆王。以其恃心以外天下之理也。先师平生为学。其大法政在存心以穷天下之理矣。其归岂特燕越之相远哉。(向呈心说源委一篇。叙列古来诸圣贤心说。而其中以孟子生之谓性。程子释氏本心二章备数者。盖欲令后之说心者。知有此科臼而审于拣别而已。初非敢为讥讽先师而设。而下教有云云。皇悚皇悚。)是故世之传诵讲说者。虽其所见之异而不能相从者。犹言其主理之苦心。不可以不深体之。亦可见自然之公情也。彼先有一物于胸中而不究本指。惟事抑勒者。又何足深较哉。妄窃以为今日为先师之徒者。政宜就先师平日讲说本指。悉心致详。以明其说心。固有以理言。有以气言。而实则以理言心者为断案。虽曰以理断心。而实则与认气为理者。毫釐而千里。此是第一机要。而先生于此。或未及周念。顾乃泛就题目上。费力迁就。以为远避人疑之计。其有持难而不能遽从者。则以为是置吾师于认气为理之科。而罪之甚重。至以为师伸冤
心。君子有不心者焉。曰释氏所谓心。是吾儒所谓形而下者。然则其以理断心者。虽其辨位正名之或欠平实。而谓是认气为理。则大不著题矣。且吾儒之所以深斥告子释氏者。为其不分形气性命。而混谓之性。混谓之道也。先师平生讲道。其宗旨专在剖判此两路矣。陆王之为陆王。以其恃心以外天下之理也。先师平生为学。其大法政在存心以穷天下之理矣。其归岂特燕越之相远哉。(向呈心说源委一篇。叙列古来诸圣贤心说。而其中以孟子生之谓性。程子释氏本心二章备数者。盖欲令后之说心者。知有此科臼而审于拣别而已。初非敢为讥讽先师而设。而下教有云云。皇悚皇悚。)是故世之传诵讲说者。虽其所见之异而不能相从者。犹言其主理之苦心。不可以不深体之。亦可见自然之公情也。彼先有一物于胸中而不究本指。惟事抑勒者。又何足深较哉。妄窃以为今日为先师之徒者。政宜就先师平日讲说本指。悉心致详。以明其说心。固有以理言。有以气言。而实则以理言心者为断案。虽曰以理断心。而实则与认气为理者。毫釐而千里。此是第一机要。而先生于此。或未及周念。顾乃泛就题目上。费力迁就。以为远避人疑之计。其有持难而不能遽从者。则以为是置吾师于认气为理之科。而罪之甚重。至以为师伸冤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2L 页
 等语。累形于文字。无乃反有隐讳之嫌而益致外人之疑耶。且念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众人之见识易差。毕竟先师之于心字名位。安知其不得千古之正案。而后辈之区区追补者。又安能自保其不出于廊柱之再数耶。今于师说。若存其真面而巽辞传疑。则后之君子容有折衷归正之路。若遽迁就指意。泯然同己。则虽得折衷之公眼。顾安所考检耶。凡此数端。皆关系甚重。极有不可苟者。伏乞深思永念而处之焉。抑有一说焉。昔静庵先生儿时。谏寒暄骂婢曰。养亲之诚虽切。君子辞气。不可不省察也。重教常敬慕此事。愿效之而未能也。今伏读下书。结辞曰先师之冤。一向莫伸。则其义安得。黾勉保合。不识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千万皇悚。以为师冤二字。元是与本事万不相称。而又以此之故。遽示割恩断义之意。无乃煞重而伤急乎。尊师之诚虽切。君子辞气。不可不审慎也。况在大贤门庭。论道讲义之体。又百世人之所瞻仰。惟先生念哉。
等语。累形于文字。无乃反有隐讳之嫌而益致外人之疑耶。且念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众人之见识易差。毕竟先师之于心字名位。安知其不得千古之正案。而后辈之区区追补者。又安能自保其不出于廊柱之再数耶。今于师说。若存其真面而巽辞传疑。则后之君子容有折衷归正之路。若遽迁就指意。泯然同己。则虽得折衷之公眼。顾安所考检耶。凡此数端。皆关系甚重。极有不可苟者。伏乞深思永念而处之焉。抑有一说焉。昔静庵先生儿时。谏寒暄骂婢曰。养亲之诚虽切。君子辞气。不可不省察也。重教常敬慕此事。愿效之而未能也。今伏读下书。结辞曰先师之冤。一向莫伸。则其义安得。黾勉保合。不识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千万皇悚。以为师冤二字。元是与本事万不相称。而又以此之故。遽示割恩断义之意。无乃煞重而伤急乎。尊师之诚虽切。君子辞气。不可不审慎也。况在大贤门庭。论道讲义之体。又百世人之所瞻仰。惟先生念哉。心性物则之说。亦有两端。一是以神明与仁义对分者也。一是以火脏与仁义对分者也。下一端。先师文集中往往有之。上一端则截然无之。其故何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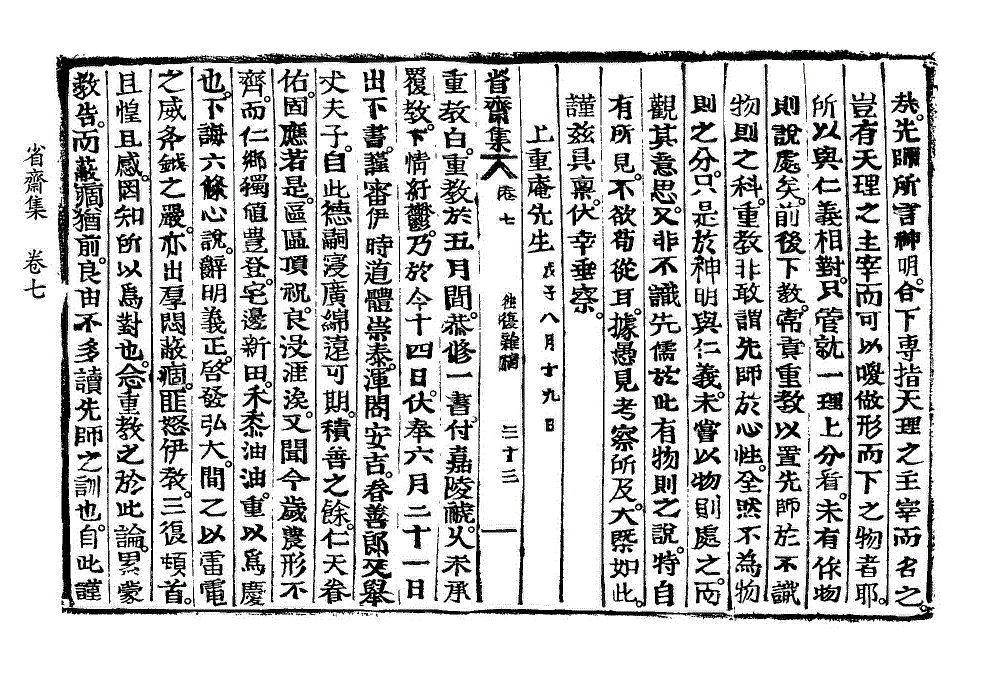 哉。先师所言神明。合下专指天理之主宰而名之。岂有天理之主宰而可以唤做形而下之物者耶。所以与仁义相对。只管就一理上分看。未有作物则说处矣。前后下教。常责重教以置先师于不识物则之科。重教非敢谓先师于心性。全然不为物则之分。只是于神明与仁义。未尝以物则处之。而观其意思。又非不识先儒于此有物则之说。特自有所见。不欲苟从耳。据愚见考察所及。大槩如此。谨玆具禀。伏幸垂察。
哉。先师所言神明。合下专指天理之主宰而名之。岂有天理之主宰而可以唤做形而下之物者耶。所以与仁义相对。只管就一理上分看。未有作物则说处矣。前后下教。常责重教以置先师于不识物则之科。重教非敢谓先师于心性。全然不为物则之分。只是于神明与仁义。未尝以物则处之。而观其意思。又非不识先儒于此有物则之说。特自有所见。不欲苟从耳。据愚见考察所及。大槩如此。谨玆具禀。伏幸垂察。上重庵先生(戊子八月十九日)
重教白。重教于五月间。恭修一书。付嘉陵褫。久未承覆教。下情纡郁。乃于今十四日。伏奉六月二十一日出下书。谨审伊时道体崇泰。浑閤安吉。春善郎又举丈夫子。自此德嗣寖广绵远可期。积善之馀。仁天眷佑。固应若是。区区顶祝。良没涯涘。又闻今岁农形不齐。而仁乡独值礼登。宅边新田。禾黍油油。重以为庆也。下诲六条心说。辞明义正。启发弘大。间之以雷电之威斧钺之严。亦出厚闷蔽痼。匪怒伊教。三复顿首。且惶且感。罔知所以为对也。念重教之于此论。累蒙教告。而蔽痼犹前。良由不多读先师之训也。自此谨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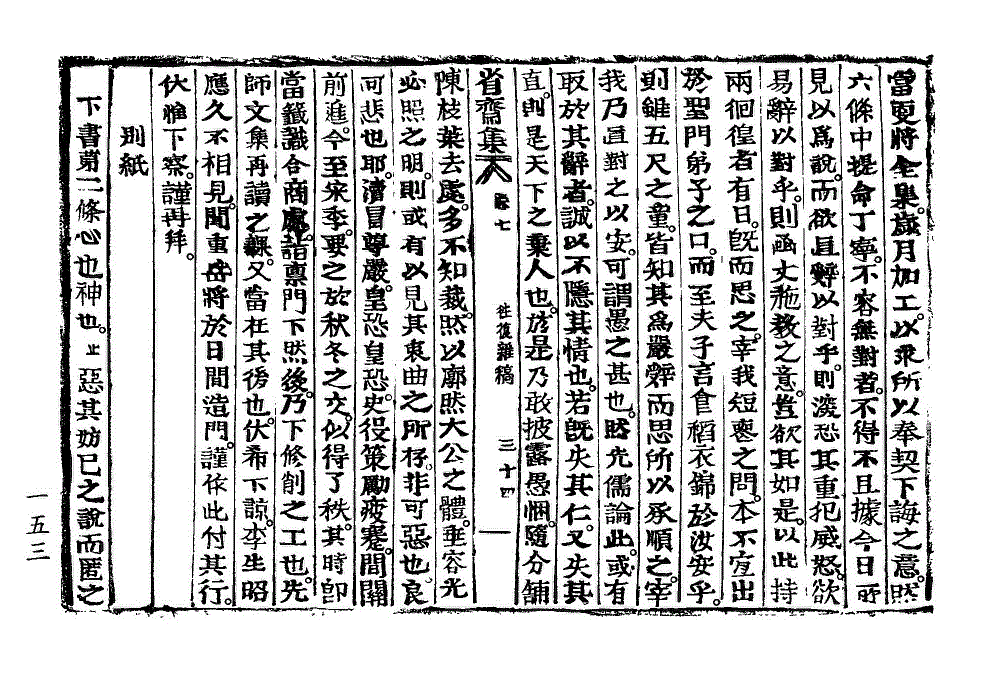 当更将全集。岁月加工。以求所以奉契下诲之意。然六条中提命丁宁。不容无对者。不得不且据今日所见以为说。而欲直辞以对乎。则深恐其重犯威怒。欲易辞以对乎。则函丈施教之意。岂欲其如是。以此持两徊徨者有日。既而思之。宰我短丧之问。本不宜出于圣门弟子之口。而至夫子言食稻衣锦于汝安乎。则虽五尺之童。皆知其为严辞而思所以承顺之。宰我乃直对之以安。可谓愚之甚也。然先儒论此。或有取于其辞者。诚以不隐其情也。若既失其仁。又失其直。则是天下之弃人也。于是乃敢披露愚悃。随分铺陈枝叶去处。多不知裁。然以廓然大公之体。垂容光必照之明。则或有以见其衷曲之所存。非可恶也。良可悲也耶。渎冒尊严。皇恐皇恐。史役策励疲蹇。间关前进。今至宋季。要之于秋冬之交。似得了秩。其时即当签识合商处。诣禀门下然后。乃下修削之工也。先师文集再读之课。又当在其后也。伏希下谅。李生昭应久不相见。闻重岳将于日间造门。谨作此付其行。伏惟下察。谨再拜。
当更将全集。岁月加工。以求所以奉契下诲之意。然六条中提命丁宁。不容无对者。不得不且据今日所见以为说。而欲直辞以对乎。则深恐其重犯威怒。欲易辞以对乎。则函丈施教之意。岂欲其如是。以此持两徊徨者有日。既而思之。宰我短丧之问。本不宜出于圣门弟子之口。而至夫子言食稻衣锦于汝安乎。则虽五尺之童。皆知其为严辞而思所以承顺之。宰我乃直对之以安。可谓愚之甚也。然先儒论此。或有取于其辞者。诚以不隐其情也。若既失其仁。又失其直。则是天下之弃人也。于是乃敢披露愚悃。随分铺陈枝叶去处。多不知裁。然以廓然大公之体。垂容光必照之明。则或有以见其衷曲之所存。非可恶也。良可悲也耶。渎冒尊严。皇恐皇恐。史役策励疲蹇。间关前进。今至宋季。要之于秋冬之交。似得了秩。其时即当签识合商处。诣禀门下然后。乃下修削之工也。先师文集再读之课。又当在其后也。伏希下谅。李生昭应久不相见。闻重岳将于日间造门。谨作此付其行。伏惟下察。谨再拜。别纸
下书第二条心也神也。(止)恶其妨己之说而匿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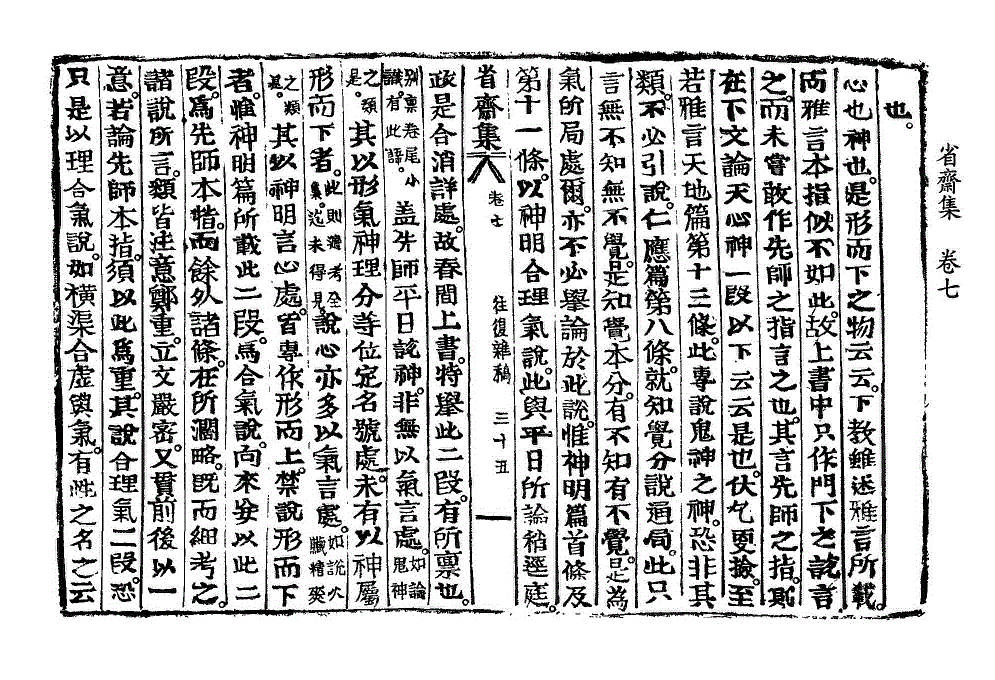 也。
也。心也神也。是形而下之物云云。下教虽述雅言所载。而雅言本指似不如此。故上书中只作门下之说言之。而未尝敢作先师之指言之也。其言先师之指。则在下文论天心神一段以下云云是也。伏乞更捡。至若雅言天地篇第十三条。此专说鬼神之神。恐非其类。不必引说。仁应篇第八条。就知觉分说通局。此只言无不知无不觉。是知觉本分。有不知有不觉。是为气所局处尔。亦不必举论于此说。惟神明篇首条及第十一条。以神明合理气说。此与平日所论稍径庭。政是合消详处。故春间上书。特举此二段。有所禀也。(别禀卷尾小识。有此语。)盖先师平日说神。非无以气言处。(如论鬼神之类是。)其以形气神理分等位定名号处。未有以神属形而下者。(此则遍考全集。迄未得见。)说心亦多以气言处。(如说火脏精爽之类是。)其以神明言心处。皆专作形而上。禁说形而下者。惟神明篇所载此二段。为合气说。向来妄以此二段。为先师本指。而馀外诸条。在所阔略。既而细考之。诸说所言。类皆注意郑重。立文严密。又贯前后以一意。若论先师本指。须以此为重。其说合理气二段。恐只是以理合气说。如横渠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之云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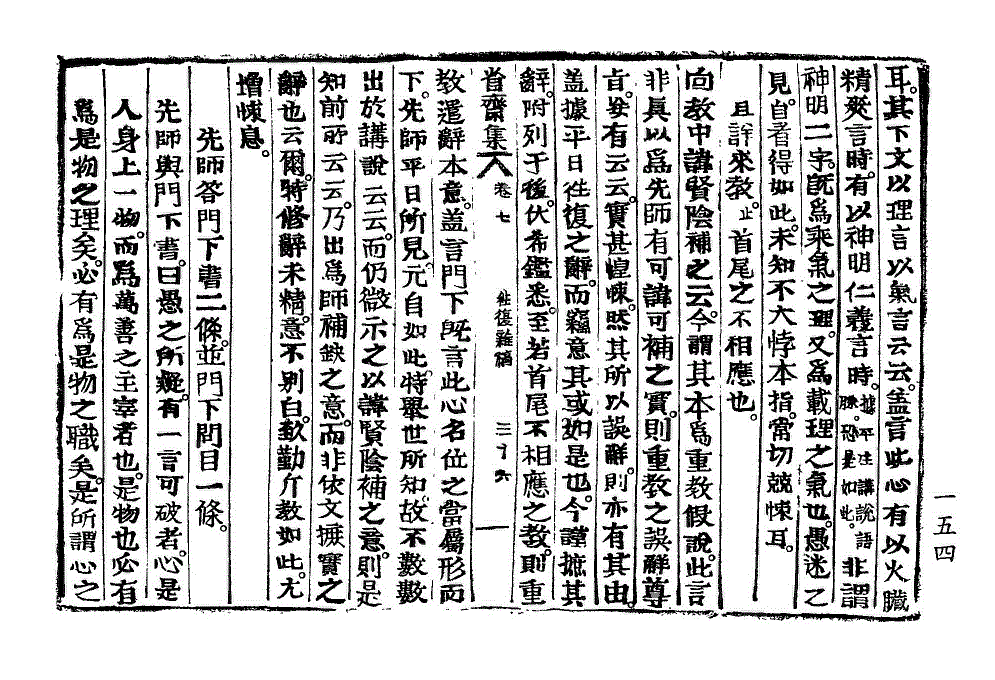 耳。其下文以理言以气言云云。盖言此心有以火脏精爽言时。有以神明仁义言时。(据平生讲说语脉。恐是如此。)非谓神明二字。既为乘气之理。又为载理之气也。愚迷之见。自看得如此。未知不大悖本指。常切兢悚耳。
耳。其下文以理言以气言云云。盖言此心有以火脏精爽言时。有以神明仁义言时。(据平生讲说语脉。恐是如此。)非谓神明二字。既为乘气之理。又为载理之气也。愚迷之见。自看得如此。未知不大悖本指。常切兢悚耳。且详来教。(止)首尾之不相应也。
向教中讳贤阴补之云。今谓其本为重教假说。此言非真以为先师有可讳可补之实。则重教之误解尊旨。妄有云云。实甚惶悚。然其所以误解。则亦有其由。盖据平日往复之辞。而窃意其或如是也。今谨摭其辞。附列于后。伏希鉴悉。至若首尾不相应之教。则重教遣辞本意。盖言门下既言此心名位之当属形而下。先师平日所见。元自如此。特举世所知。故不数数出于讲说云云。而仍微示之以讳贤阴补之意。则是知前所云云。乃出为师补缺之意。而非依文摭实之辞也云尔。特修辞未精。意不别白。致勤斤教如此。尤增悚息。
先师答门下书二条。并门下问目一条。
先师与门下书。曰愚之所疑。有一言可破者。心是人身上一物。而为万善之主宰者也。是物也必有为是物之理矣。必有为是物之职矣。是所谓心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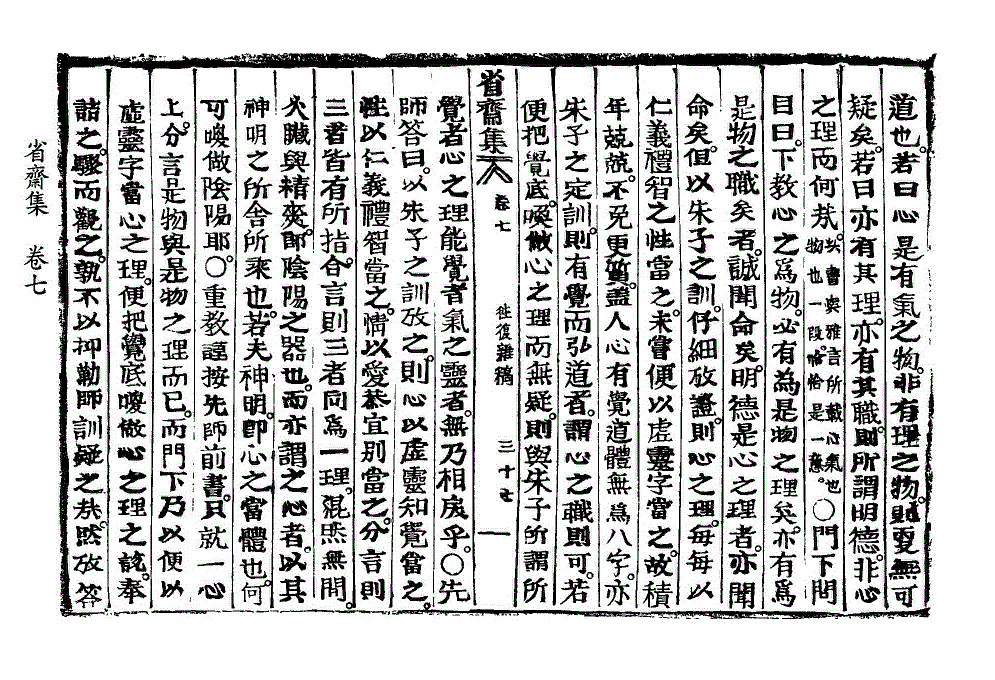 道也。若曰心是有气之物。非有理之物。则更无可疑矣。若曰亦有其理。亦有其职。则所谓明德。非心之理而何哉。(此书与雅言所载心气也物也一段。恰恰是一意。)○门下问目曰。下教心之为物。必有为是物之理矣。亦有为是物之职矣者。诚闻命矣。明德是心之理者。亦闻命矣。但以朱子之训。仔细考證。则心之理。每每以仁义礼智之性当之。未尝便以虚灵字当之。故积年兢兢。不免更质。盖人心有觉道体无为八字。亦朱子之定训。则有觉而弘道者。谓心之职则可。若便把觉底。唤做心之理而无疑。则与朱子所谓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者。无乃相戾乎。○先师答曰。以朱子之训考之。则心以虚灵知觉当之。性以仁义礼智当之。情以爱恭宜别当之。分言则三者皆有所指。合言则三者同为一理。混然无间。火脏与精爽。即阴阳之器也。而亦谓之心者。以其神明之所舍所乘也。若夫神明。即心之当体也。何可唤做阴阳耶。○重教谨按先师前书。只就一心上。分言是物与是物之理而已。而门下乃以便以虚灵字当心之理。便把觉底唤做心之理之说。奉诘之。骤而观之。孰不以抑勒师训疑之哉。然考答
道也。若曰心是有气之物。非有理之物。则更无可疑矣。若曰亦有其理。亦有其职。则所谓明德。非心之理而何哉。(此书与雅言所载心气也物也一段。恰恰是一意。)○门下问目曰。下教心之为物。必有为是物之理矣。亦有为是物之职矣者。诚闻命矣。明德是心之理者。亦闻命矣。但以朱子之训。仔细考證。则心之理。每每以仁义礼智之性当之。未尝便以虚灵字当之。故积年兢兢。不免更质。盖人心有觉道体无为八字。亦朱子之定训。则有觉而弘道者。谓心之职则可。若便把觉底。唤做心之理而无疑。则与朱子所谓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者。无乃相戾乎。○先师答曰。以朱子之训考之。则心以虚灵知觉当之。性以仁义礼智当之。情以爱恭宜别当之。分言则三者皆有所指。合言则三者同为一理。混然无间。火脏与精爽。即阴阳之器也。而亦谓之心者。以其神明之所舍所乘也。若夫神明。即心之当体也。何可唤做阴阳耶。○重教谨按先师前书。只就一心上。分言是物与是物之理而已。而门下乃以便以虚灵字当心之理。便把觉底唤做心之理之说。奉诘之。骤而观之。孰不以抑勒师训疑之哉。然考答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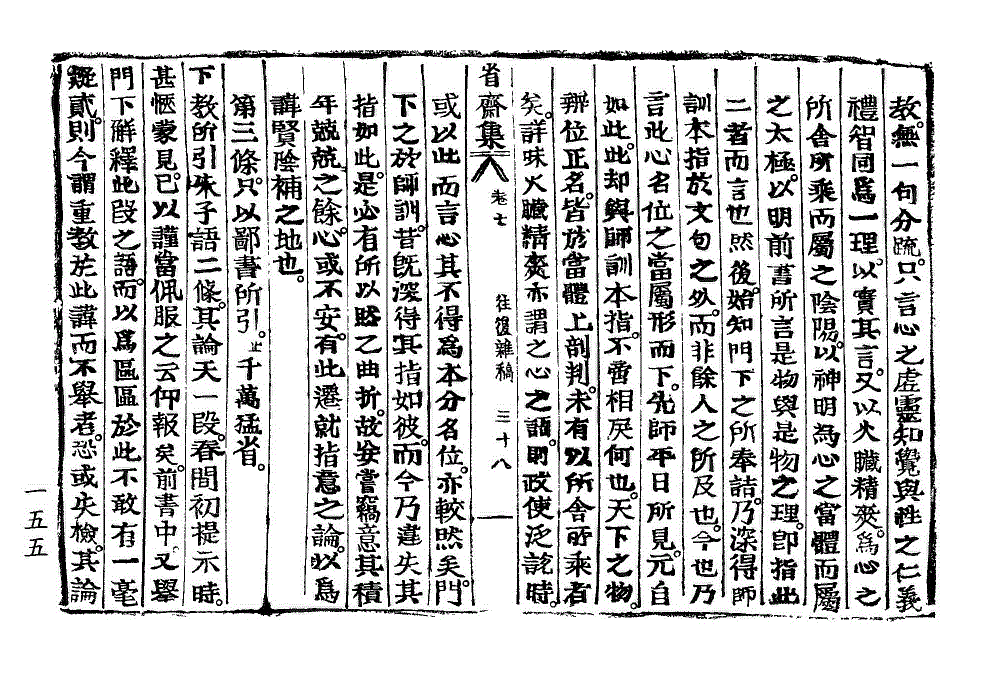 教。无一句分疏。只言心之虚灵知觉与性之仁义礼智同为一理。以实其言。又以火脏精爽。为心之所舍所乘而属之阴阳。以神明为心之当体而属之太极。以明前书所言是物与是物之理。即指此二者而言也然后。始知门下之所奉诘。乃深得师训本指于文句之外。而非馀人之所及也。今也乃言此心名位之当属形而下。先师平日所见。元自如此。此却与师训本指。不啻相戾何也。天下之物。辨位正名。皆于当体上剖判。未有以所舍所乘者矣。详味火脏精爽亦谓之心之语。则政使泛说时。或以此而言心其不得为本分名位。亦较然矣。门下之于师训。昔既深得其指如彼。而今乃违失其指如此。是必有所以然之曲折。故妄尝窃意其积年兢兢之馀。心或不安。有此迁就指意之论。以为讳贤阴补之地也。
教。无一句分疏。只言心之虚灵知觉与性之仁义礼智同为一理。以实其言。又以火脏精爽。为心之所舍所乘而属之阴阳。以神明为心之当体而属之太极。以明前书所言是物与是物之理。即指此二者而言也然后。始知门下之所奉诘。乃深得师训本指于文句之外。而非馀人之所及也。今也乃言此心名位之当属形而下。先师平日所见。元自如此。此却与师训本指。不啻相戾何也。天下之物。辨位正名。皆于当体上剖判。未有以所舍所乘者矣。详味火脏精爽亦谓之心之语。则政使泛说时。或以此而言心其不得为本分名位。亦较然矣。门下之于师训。昔既深得其指如彼。而今乃违失其指如此。是必有所以然之曲折。故妄尝窃意其积年兢兢之馀。心或不安。有此迁就指意之论。以为讳贤阴补之地也。第三条。只以鄙书所引。(止)千万猛省。
下教所引朱子语二条。其论天一段。春间初提示时。甚惬蒙见。已以谨当佩服之云仰报矣。前书中。又举门下解释此段之语。而以为区区于此不敢有一毫疑贰。则今谓重教于此讳而不举者。恐或失检。其论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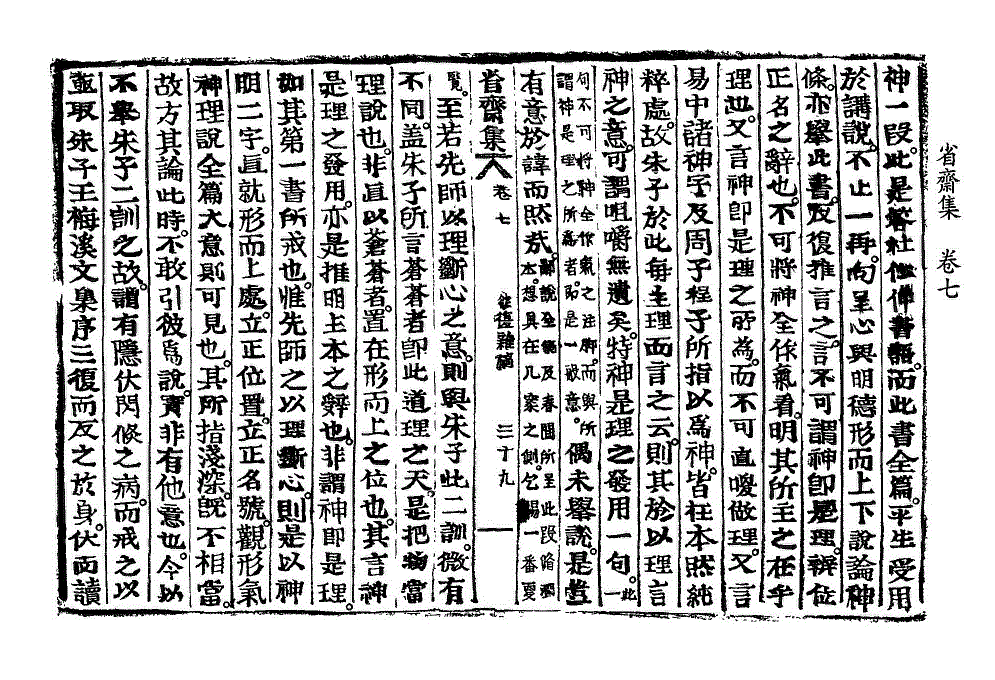 神一段。此是答杜仁仲书语。而此书全篇。平生受用于讲说。不止一再。向呈心与明德形而上下说论神条。亦举此书。反复推言之。言不可谓神即是理。辨位正名之辞也。不可将神全作气看。明其所主之在乎理也。又言神即是理之所为。而不可直唤做理。又言易中诸神字及周子程子所指以为神。皆在本然纯粹处。故朱子于此每主理而言之云。则其于以理言神之意。可谓咀嚼无遗矣。特神是理之发用一句。(此一句不可将神全作气之注脚。而与所谓神是理之所为者。即是一般意。)偶未举说。是岂有意于讳而然哉。(鄙说全稿及春间所呈此段脩润本。想具在几案之侧。乞赐一番更览。)至若先师以理断心之意。则与朱子此二训。微有不同。盖朱子所言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是把物当理说也。非直以苍苍者。置在形而上之位也。其言神是理之发用。亦是推明主本之辞也。非谓神即是理。如其第一书所戒也。惟先师之以理断心。则是以神明二字。直就形而上处。立正位置。立正名号。观形气神理说全篇大意则可见也。其所指浅深。既不相当。故方其论此时。不敢引彼为说。实非有他意也。今以不举朱子二训之故。谓有隐伏闪倏之病。而戒之以亟取朱子王梅溪文集序三复而反之于身。伏而读
神一段。此是答杜仁仲书语。而此书全篇。平生受用于讲说。不止一再。向呈心与明德形而上下说论神条。亦举此书。反复推言之。言不可谓神即是理。辨位正名之辞也。不可将神全作气看。明其所主之在乎理也。又言神即是理之所为。而不可直唤做理。又言易中诸神字及周子程子所指以为神。皆在本然纯粹处。故朱子于此每主理而言之云。则其于以理言神之意。可谓咀嚼无遗矣。特神是理之发用一句。(此一句不可将神全作气之注脚。而与所谓神是理之所为者。即是一般意。)偶未举说。是岂有意于讳而然哉。(鄙说全稿及春间所呈此段脩润本。想具在几案之侧。乞赐一番更览。)至若先师以理断心之意。则与朱子此二训。微有不同。盖朱子所言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是把物当理说也。非直以苍苍者。置在形而上之位也。其言神是理之发用。亦是推明主本之辞也。非谓神即是理。如其第一书所戒也。惟先师之以理断心。则是以神明二字。直就形而上处。立正位置。立正名号。观形气神理说全篇大意则可见也。其所指浅深。既不相当。故方其论此时。不敢引彼为说。实非有他意也。今以不举朱子二训之故。谓有隐伏闪倏之病。而戒之以亟取朱子王梅溪文集序三复而反之于身。伏而读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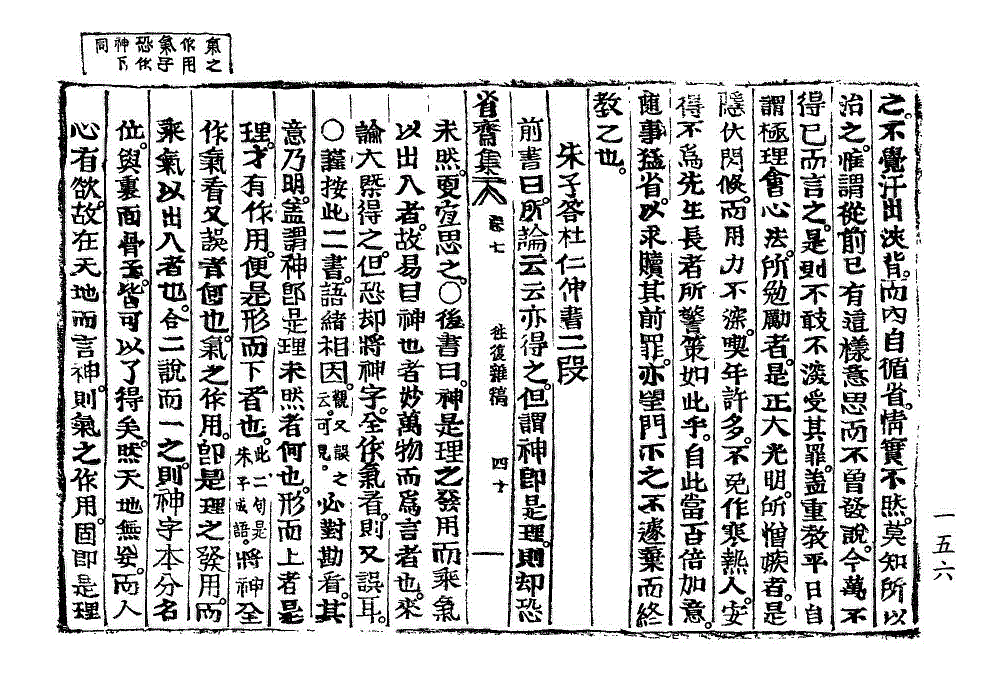 之。不觉汗出浃背。而内自循省。情实不然。莫知所以治之。惟谓从前已有这样意思而不曾发说。今万不得已而言之。是则不敢不深受其罪。盖重教平日自谓极理会心法。所勉励者。是正大光明。所憎嫉者。是隐伏闪倏。而用力不深。吃年许多。不免作寒热人。安得不为先生长者所警策如此乎。自此当百倍加意。随事猛省。以求赎其前罪。亦望门下之不遽弃而终教之也。
之。不觉汗出浃背。而内自循省。情实不然。莫知所以治之。惟谓从前已有这样意思而不曾发说。今万不得已而言之。是则不敢不深受其罪。盖重教平日自谓极理会心法。所勉励者。是正大光明。所憎嫉者。是隐伏闪倏。而用力不深。吃年许多。不免作寒热人。安得不为先生长者所警策如此乎。自此当百倍加意。随事猛省。以求赎其前罪。亦望门下之不遽弃而终教之也。朱子答杜仁仲书二段
前书曰。所论云云亦得之。但谓神即是理。则却恐未然。更宜思之。○后书曰。神是理之发用而乘气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来谕大槩得之。但恐却将神字。全作气看。则又误耳。○谨按此二书。语绪相因。(观又误之云。可见。)必对勘看。其意乃明。盖谓神即是理未然者何也。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也。(此二句是朱子成语。)将神全作气看又误者何也。气之作用。(气之作用气字。恐作神。下同。)即是理之发用。而乘气以出入者也。合二说而一之。则神字本分名位。与里面骨子。皆可以了得矣。然天地无妄。而人心有欲。故在天地而言神。则气之作用。固即是理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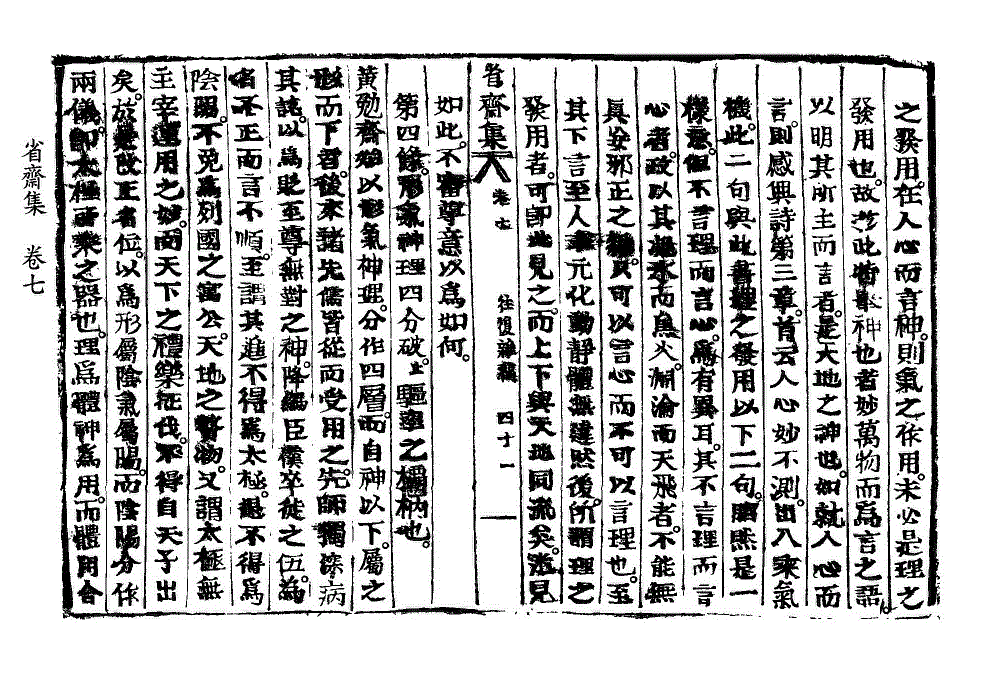 之发用。在人心而言神。则气之作用。未必是理之发用也。故于此特举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之语。以明其所主而言者。是天地之神也。如就人心而言。则感兴诗第三章。首云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此二句与此书理之发用以下二句。吻然是一样意。但不言理而言心。为有异耳。其不言理而言心者。政以其凝冰而焦火。渊沦而天飞者。不能无真妄邪正之杂。只可以言心而不可以言理也。至其下言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然后。所谓理之发用者。可即此见之。而上下与天地同流矣。迷见如此。不审尊意以为如何。
之发用。在人心而言神。则气之作用。未必是理之发用也。故于此特举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之语。以明其所主而言者。是天地之神也。如就人心而言。则感兴诗第三章。首云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此二句与此书理之发用以下二句。吻然是一样意。但不言理而言心。为有异耳。其不言理而言心者。政以其凝冰而焦火。渊沦而天飞者。不能无真妄邪正之杂。只可以言心而不可以言理也。至其下言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然后。所谓理之发用者。可即此见之。而上下与天地同流矣。迷见如此。不审尊意以为如何。第四条。形气神理四分破。(止)驱率之把柄也。
黄勉斋始以形气神理。分作四层。而自神以下。属之形而下者。后来诸先儒皆从而受用之。先师独深病其说。以为贬至尊无对之神。降编臣仆卒徒之伍。为名不正而言不顺。至谓其进不得为太极。退不得为阴阳。不免为列国之寓公。天地之赘物。又谓太极无主宰运用之妙。而天下之礼乐征伐。不得自天子出矣。于是改正名位。以为形属阴气属阳。而阴阳分作两仪。即太极所乘之器也。理为体神为用。而体用合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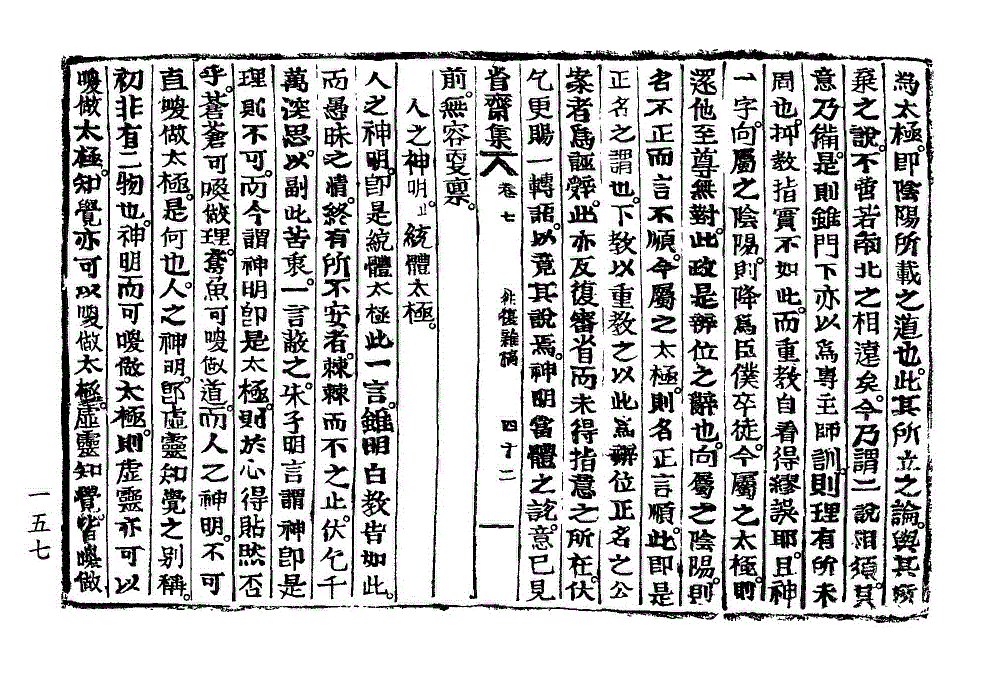 为太极。即阴阳所载之道也。此其所立之论。与其所弃之说。不啻若南北之相远矣。今乃谓二说相须。其意乃备。是则虽门下亦以为专主师训。则理有所未周也。抑教指实不如此。而重教自看得缪误耶。且神一字。向属之阴阳。则降为臣仆卒徒。今属之太极。则还他至尊无对。此政是辨位之辞也。向属之阴阳。则名不正而言不顺。今属之太极。则名正言顺。此即是正名之谓也。下教以重教之以此为辨位正名之公案者为诬辞。此亦反复审省而未得指意之所在。伏乞更赐一转语。以竟其说焉。神明当体之说。意已见前。无容更禀。
为太极。即阴阳所载之道也。此其所立之论。与其所弃之说。不啻若南北之相远矣。今乃谓二说相须。其意乃备。是则虽门下亦以为专主师训。则理有所未周也。抑教指实不如此。而重教自看得缪误耶。且神一字。向属之阴阳。则降为臣仆卒徒。今属之太极。则还他至尊无对。此政是辨位之辞也。向属之阴阳。则名不正而言不顺。今属之太极。则名正言顺。此即是正名之谓也。下教以重教之以此为辨位正名之公案者为诬辞。此亦反复审省而未得指意之所在。伏乞更赐一转语。以竟其说焉。神明当体之说。意已见前。无容更禀。人之神明。(止)统体太极。
人之神明。即是统体太极此一言。虽明白教告如此。而愚昧之情。终有所不安者。棘棘而不之止。伏乞千万深思。以副此苦衷。一言蔽之。朱子明言谓神即是理则不可。而今谓神明即是太极。则于心得贴然否乎。苍苍可唤做理。鸢鱼可唤做道。而人之神明。不可直唤做太极。是何也。人之神明。即虚灵知觉之别称。初非有二物也。神明而可唤做太极。则虚灵亦可以唤做太极。知觉亦可以唤做太极。虚灵知觉。皆唤做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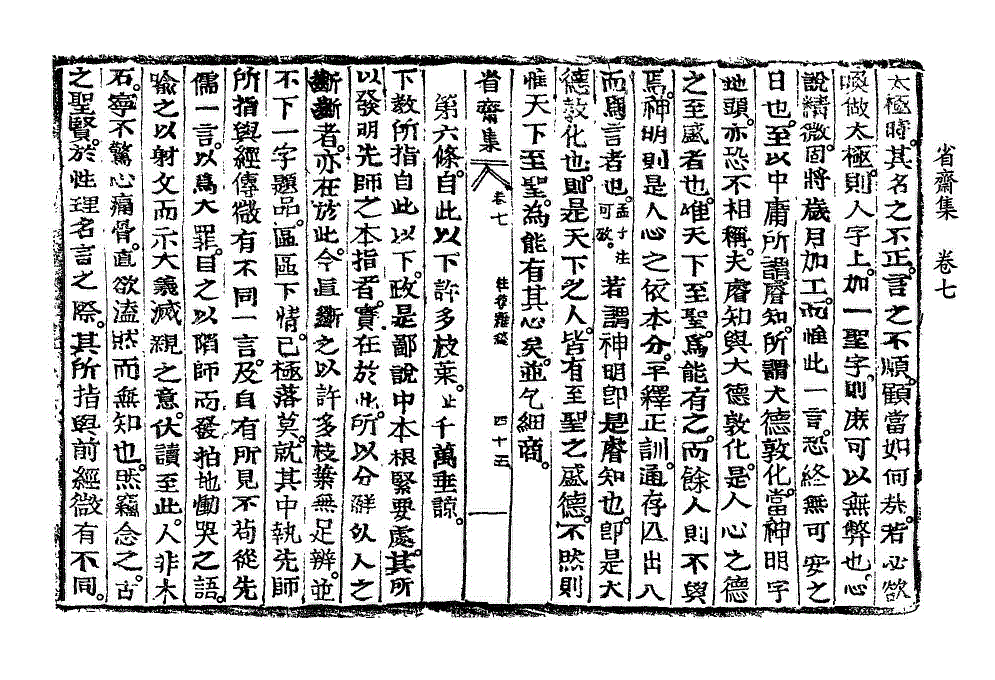 太极时。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顺。顾当如何哉。若必欲唤做太极。则人字上。加一圣字。则庶可以无弊也。心说精微。固将岁月加工。而惟此一言。恐终无可安之日也。至以中庸所谓睿知。所谓大德敦化。当神明字地头。亦恐不相称。夫睿知与大德敦化。是人心之德之至盛者也。唯天下至圣。为能有之。而馀人则不与焉。神明则是人心之依本分。平释正训。通存亡出入而为言者也。(孟子注可考。)若谓神明即是睿知也。即是大德教化也。则是天下之人。皆有至圣之盛德。不然则惟天下至圣。为能有其心矣。并乞细商。
太极时。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顺。顾当如何哉。若必欲唤做太极。则人字上。加一圣字。则庶可以无弊也。心说精微。固将岁月加工。而惟此一言。恐终无可安之日也。至以中庸所谓睿知。所谓大德敦化。当神明字地头。亦恐不相称。夫睿知与大德敦化。是人心之德之至盛者也。唯天下至圣。为能有之。而馀人则不与焉。神明则是人心之依本分。平释正训。通存亡出入而为言者也。(孟子注可考。)若谓神明即是睿知也。即是大德教化也。则是天下之人。皆有至圣之盛德。不然则惟天下至圣。为能有其心矣。并乞细商。第六条。自此以下许多枝叶。(止)千万垂谅。
下教所指自此以下。政是鄙说中本根紧要处。其所以发明先师之本指者。实在于此。所以分解外人之龂龂者。亦在于此。今直断之以许多枝叶无足辨。并不下一字题品。区区下情。已极落莫。就其中执先师所指与经传微有不同一言。及自有所见不苟从先儒一言。以为大罪。目之以陷师而发拍地恸哭之语。喻之以射父而示大义灭亲之意。伏读至此。人非木石。宁不惊心痛骨。直欲溘然而无知也。然窃念之。古之圣贤。于性理名言之际。其所指与前经微有不同。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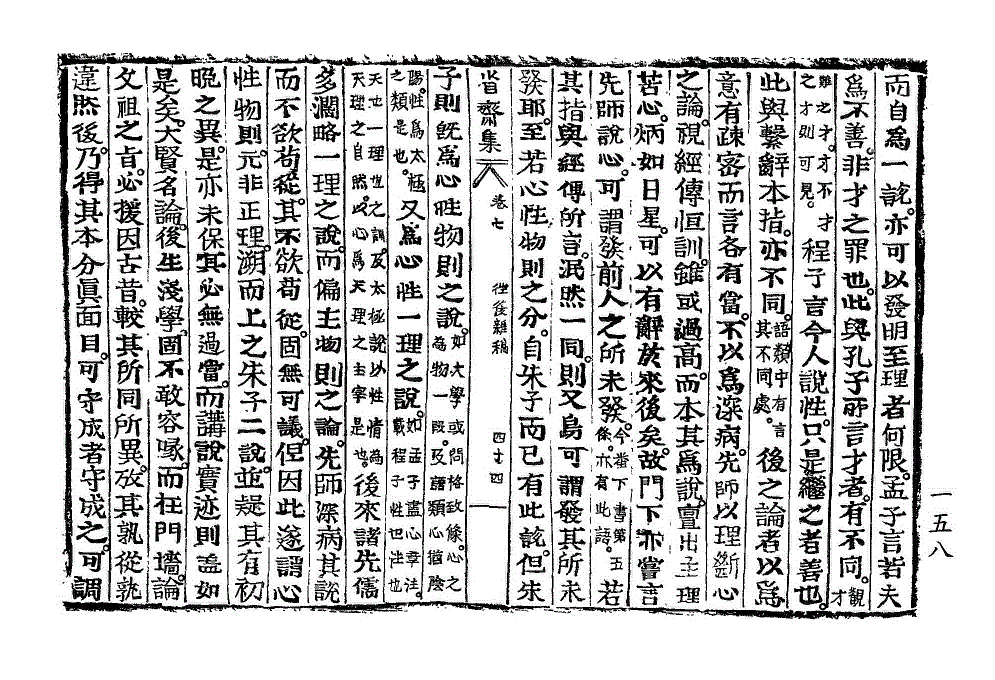 而自为一说。亦可以发明至理者何限。孟子言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与孔子所言才者。有不同。(观才难之才。才不才之才则可见。)程子言今人说性。只是继之者善也。此与系辞本指。亦不同。(语类中有言其不同处。)后之论者以为意有疏密而言各有当。不以为深病。先师以理断心之论。视经传恒训。虽或过高。而本其为说。亶出主理苦心。炳如日星。可以有辞于来后矣。故门下亦尝言先师说心。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今番下书第五条。亦有此语。)若其指与经传所言。泯然一同。则又乌可谓发其所未发耶。至若心性物则之分。自朱子而已有此说。但朱子则既为心性物则之说。(如大学或问格致条。心之为物一段。及语类心犹阴阳。性为太极之类是也。)又为心性一理之说。如孟子尽心章注。载程子性(《二程遗书》 卷25 〈畅潜道本〉 등에 의하면 "心"의 오기이다.)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之训。及太极说以性情为天理之自然。以心为天理之主宰是也。 后来诸先儒多阔略一理之说。而偏主物则之论。先师深病其说而不欲苟从。其不欲苟从。固无可议。但因此遂谓心性物则。元非正理。溯而上之朱子二说。并疑其有初晚之异。是亦未保其必无过当。而讲说实迹则盖如是矣。大贤名论。后生浅学。固不敢容喙。而在门墙。论父祖之旨。必援因古昔。较其所同所异。考其孰从孰违然后。乃得其本分真面目。可守成者守成之。可调
而自为一说。亦可以发明至理者何限。孟子言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与孔子所言才者。有不同。(观才难之才。才不才之才则可见。)程子言今人说性。只是继之者善也。此与系辞本指。亦不同。(语类中有言其不同处。)后之论者以为意有疏密而言各有当。不以为深病。先师以理断心之论。视经传恒训。虽或过高。而本其为说。亶出主理苦心。炳如日星。可以有辞于来后矣。故门下亦尝言先师说心。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今番下书第五条。亦有此语。)若其指与经传所言。泯然一同。则又乌可谓发其所未发耶。至若心性物则之分。自朱子而已有此说。但朱子则既为心性物则之说。(如大学或问格致条。心之为物一段。及语类心犹阴阳。性为太极之类是也。)又为心性一理之说。如孟子尽心章注。载程子性(《二程遗书》 卷25 〈畅潜道本〉 등에 의하면 "心"의 오기이다.)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之训。及太极说以性情为天理之自然。以心为天理之主宰是也。 后来诸先儒多阔略一理之说。而偏主物则之论。先师深病其说而不欲苟从。其不欲苟从。固无可议。但因此遂谓心性物则。元非正理。溯而上之朱子二说。并疑其有初晚之异。是亦未保其必无过当。而讲说实迹则盖如是矣。大贤名论。后生浅学。固不敢容喙。而在门墙。论父祖之旨。必援因古昔。较其所同所异。考其孰从孰违然后。乃得其本分真面目。可守成者守成之。可调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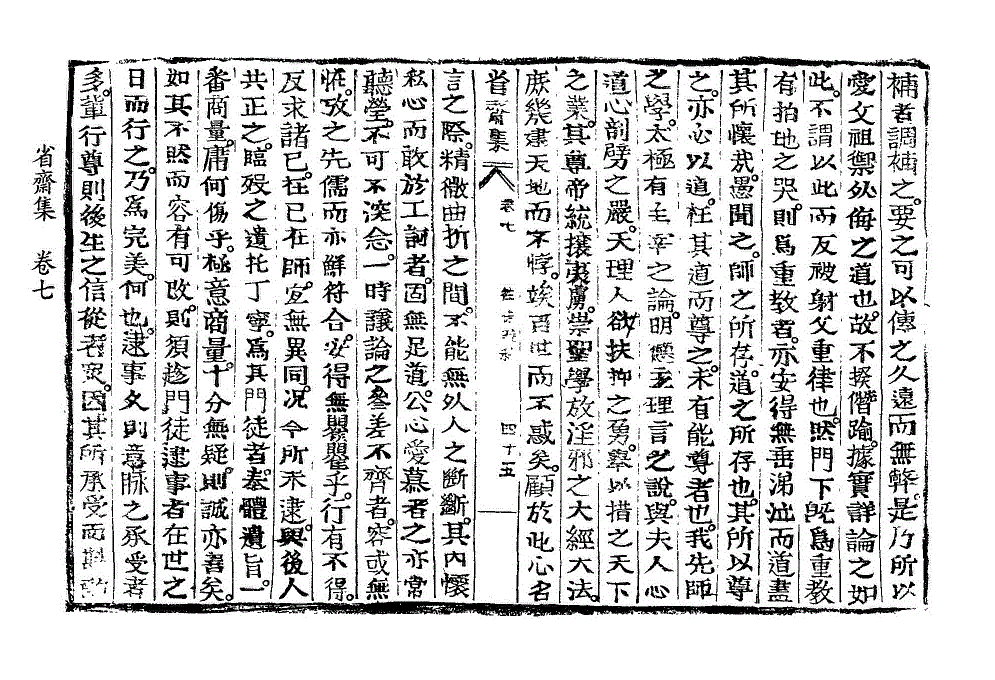 补者调补之。要之可以传之久远而无㢢。是乃所以爱父祖御外侮之道也。故不揆僭踰。据实详论之如此。不谓以此而反被射父重律也。然门下既为重教有拍地之哭。则为重教者。亦安得无垂涕泣而道尽其所怀哉。愚闻之。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所以尊之。亦必以道。枉其道而尊之。未有能尊者也。我先师之学。太极有主宰之论。明德主理言之说。与夫人心道心剖劈之严。天理人欲扶抑之勇。举以措之天下之业。其尊帝统攘夷虏。崇圣学放淫邪之大经大法。庶几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矣。顾于此心名言之际。精微曲折之间。不能无外人之断断。其内怀私心而敢于工诃者。固无足道。公心爱慕者之亦常听莹。不可不深念。一时议论之参差不齐者。容或无怪。考之先儒而亦鲜符合。安得无瞿瞿乎。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己在师。宜无异同。况今所未逮。与后人共正之。临殁之遗托丁宁。为其门徒者。奉体遗旨。一番商量。庸何伤乎。极意商量。十分无疑。则诚亦善矣。如其不然而容有可改。则须趁门徒逮事者在世之日而行之。乃为完美。何也。逮事久则意脉之承受者多。辈行尊则后生之信从者众。因其所承受而斟酌
补者调补之。要之可以传之久远而无㢢。是乃所以爱父祖御外侮之道也。故不揆僭踰。据实详论之如此。不谓以此而反被射父重律也。然门下既为重教有拍地之哭。则为重教者。亦安得无垂涕泣而道尽其所怀哉。愚闻之。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所以尊之。亦必以道。枉其道而尊之。未有能尊者也。我先师之学。太极有主宰之论。明德主理言之说。与夫人心道心剖劈之严。天理人欲扶抑之勇。举以措之天下之业。其尊帝统攘夷虏。崇圣学放淫邪之大经大法。庶几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矣。顾于此心名言之际。精微曲折之间。不能无外人之断断。其内怀私心而敢于工诃者。固无足道。公心爱慕者之亦常听莹。不可不深念。一时议论之参差不齐者。容或无怪。考之先儒而亦鲜符合。安得无瞿瞿乎。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己在师。宜无异同。况今所未逮。与后人共正之。临殁之遗托丁宁。为其门徒者。奉体遗旨。一番商量。庸何伤乎。极意商量。十分无疑。则诚亦善矣。如其不然而容有可改。则须趁门徒逮事者在世之日而行之。乃为完美。何也。逮事久则意脉之承受者多。辈行尊则后生之信从者众。因其所承受而斟酌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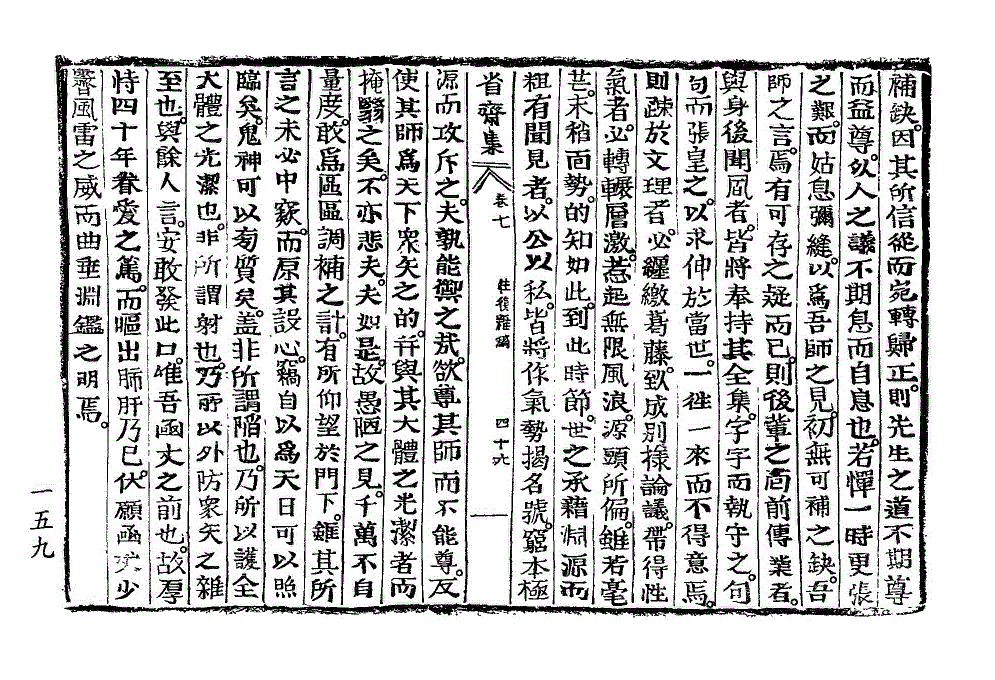 补缺。因其所信从而宛转归正。则先生之道不期尊而益尊。外人之议不期息而自息也。若惮一时更张之艰。而姑息弥缝。以为吾师之见。初无可补之缺。吾师之言。焉有可存之疑而已。则后辈之面前传业者。与身后闻风者。皆将奉持其全集。字字而执守之。句句而张皇之。以求伸于当世。一往一来而不得意焉。则疏于文理者。必缠缴葛藤。致成别㨾论议。带得性气者。必转辗层激。惹起无限风浪。源头所偏。虽若毫芒。末稍面势。的知如此。到此时节。世之承藉渊源而粗有闻见者。以公以私。皆将作气势揭名号。穷本极源而攻斥之。夫孰能御之哉。欲尊其师而不能尊。反使其师为天下众矢之的。并与其大体之光洁者而掩翳之矣。不亦悲夫。夫如是。故愚陋之见。千万不自量度。敢为区区调补之计。有所仰望于门下。虽其所言之未必中窾。而原其设心。窃自以为天日可以照临矣。鬼神可以旁质矣。盖非所谓陷也。乃所以护全大体之光洁也。非所谓射也。乃所以外防众矢之杂至也。与馀人言。安敢发此口。唯吾函丈之前也。故厚恃四十年眷爱之笃。而呕出肺肝乃已。伏愿函丈少霁风雷之威而曲垂渊鉴之明焉。
补缺。因其所信从而宛转归正。则先生之道不期尊而益尊。外人之议不期息而自息也。若惮一时更张之艰。而姑息弥缝。以为吾师之见。初无可补之缺。吾师之言。焉有可存之疑而已。则后辈之面前传业者。与身后闻风者。皆将奉持其全集。字字而执守之。句句而张皇之。以求伸于当世。一往一来而不得意焉。则疏于文理者。必缠缴葛藤。致成别㨾论议。带得性气者。必转辗层激。惹起无限风浪。源头所偏。虽若毫芒。末稍面势。的知如此。到此时节。世之承藉渊源而粗有闻见者。以公以私。皆将作气势揭名号。穷本极源而攻斥之。夫孰能御之哉。欲尊其师而不能尊。反使其师为天下众矢之的。并与其大体之光洁者而掩翳之矣。不亦悲夫。夫如是。故愚陋之见。千万不自量度。敢为区区调补之计。有所仰望于门下。虽其所言之未必中窾。而原其设心。窃自以为天日可以照临矣。鬼神可以旁质矣。盖非所谓陷也。乃所以护全大体之光洁也。非所谓射也。乃所以外防众矢之杂至也。与馀人言。安敢发此口。唯吾函丈之前也。故厚恃四十年眷爱之笃。而呕出肺肝乃已。伏愿函丈少霁风雷之威而曲垂渊鉴之明焉。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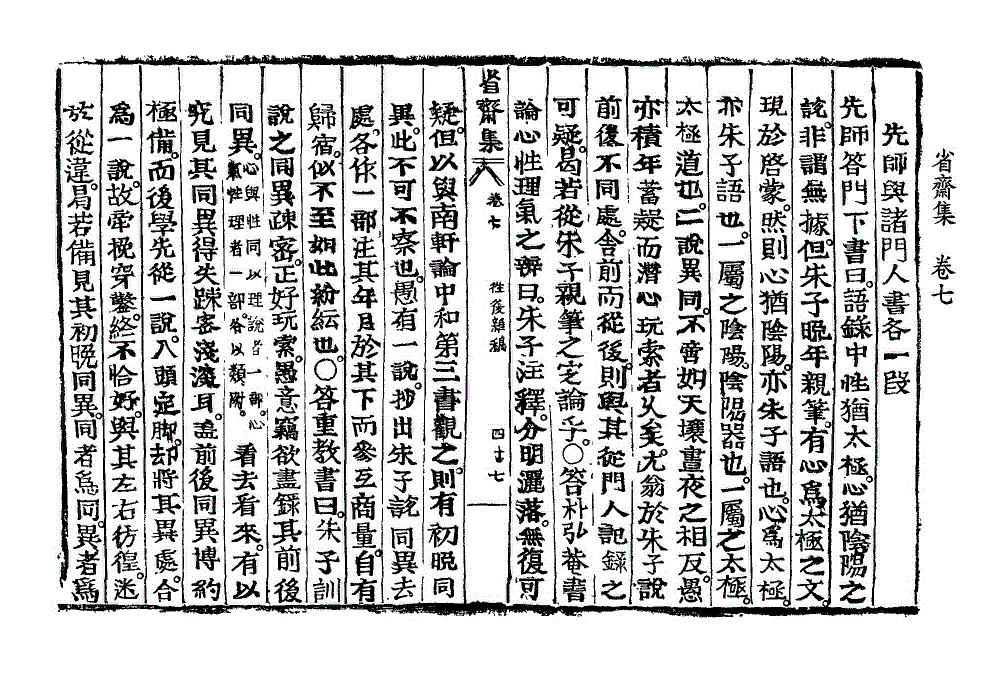 先师与诸门人书各一段
先师与诸门人书各一段先师答门下书曰。语录中性犹太极。心犹阴阳之说。非谓无据。但朱子晚年亲笔。有心为太极之文。现于启蒙。然则心犹阴阳。亦朱子语也。心为太极。亦朱子语也。一属之阴阳。阴阳器也。一属之太极。太极道也。二说异同。不啻如天壤昼夜之相反。愚亦积年蓄疑而潜心玩索者久矣。尤翁于朱子说前后不同处。舍前而从后。则与其从门人记录之可疑。曷若从朱子亲笔之定论乎。○答朴弘庵书论心性理气之辨曰。朱子注释。分明洒落。无复可疑。但以与南轩论中和第三书观之。则有初晚同异。此不可不察也。愚有一说。抄出朱子说同异去处。各作一部注其年月于其下而参互商量。自有归宿。似不至如此纷纭也。○答重教书曰。朱子训说之同异疏密。正好玩索。愚意窃欲尽录其前后同异。(心与性同以理说者一部。心气性理者一部。各以类附。)看去看来。有以究见其同异得失疏密浅深耳。盖前后同异博约极备。而后学先从一说。入头定脚。却将其异处。合为一说。故牵挽穿凿。终不恰好。与其左右彷徨。迷于从违。曷若备见其初晚同异。同者为同。异者为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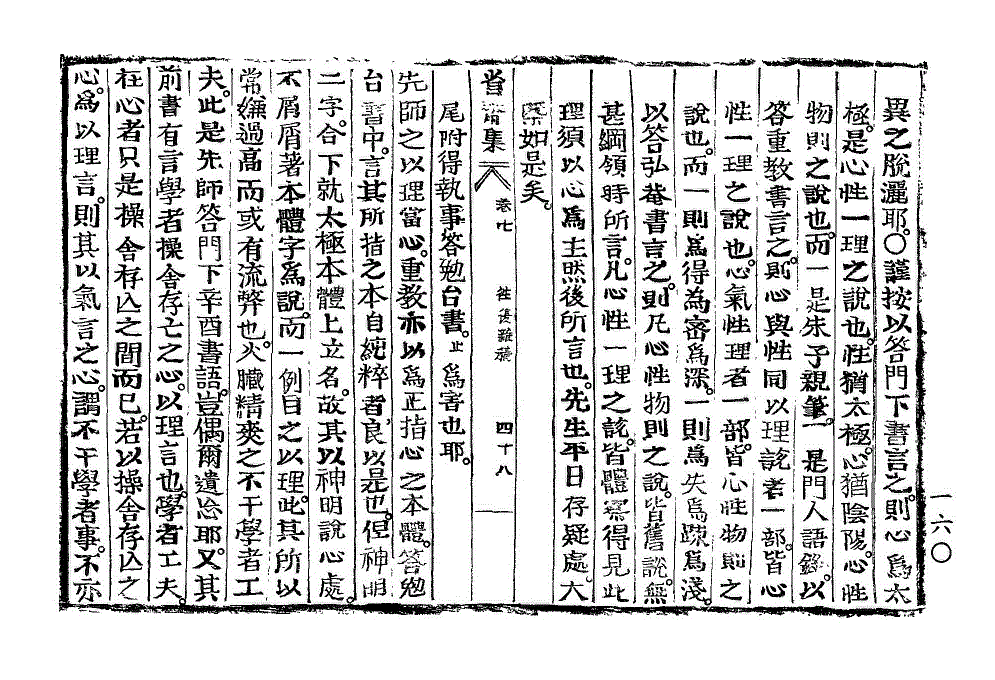 异之脱洒耶。○谨按以答门下书言之。则心为太极。是心性一理之说也。性犹太极。心犹阴阳。心性物则之说也。而一是朱子亲笔。一是门人语录。以答重教书言之。则心与性同以理说者一部。皆心性一理之说也。心气性理者一部。皆心性物则之说也。而一则为得为密为深。一则为失为疏为浅。以答弘庵书言之。则凡心性物则之说。皆旧说。无甚纲领时所言。凡心性一理之说。皆体察得见此理须以心为主然后所言也。先生平日存疑处。大槩如是矣。
异之脱洒耶。○谨按以答门下书言之。则心为太极。是心性一理之说也。性犹太极。心犹阴阳。心性物则之说也。而一是朱子亲笔。一是门人语录。以答重教书言之。则心与性同以理说者一部。皆心性一理之说也。心气性理者一部。皆心性物则之说也。而一则为得为密为深。一则为失为疏为浅。以答弘庵书言之。则凡心性物则之说。皆旧说。无甚纲领时所言。凡心性一理之说。皆体察得见此理须以心为主然后所言也。先生平日存疑处。大槩如是矣。尾附得执事答勉台书。(止)为害也耶。
先师之以理当心。重教亦以为正指心之本体。答勉台书中。言其所指之本自纯粹者。良以是也。但神明二字。合下就太极本体上立名。故其以神明说心处。不屑屑著本体字为说。而一例目之以理。此其所以常嫌过高而或有流弊也。火脏精爽之不干学者工夫。此是先师答门下辛酉书语。岂偶尔遗忘耶。又其前书有言学者操舍存亡之心。以理言也。学者工夫。在心者只是操舍存亡之间而已。若以操舍存亡之心。为以理言。则其以气言之心。谓不干学者事。不亦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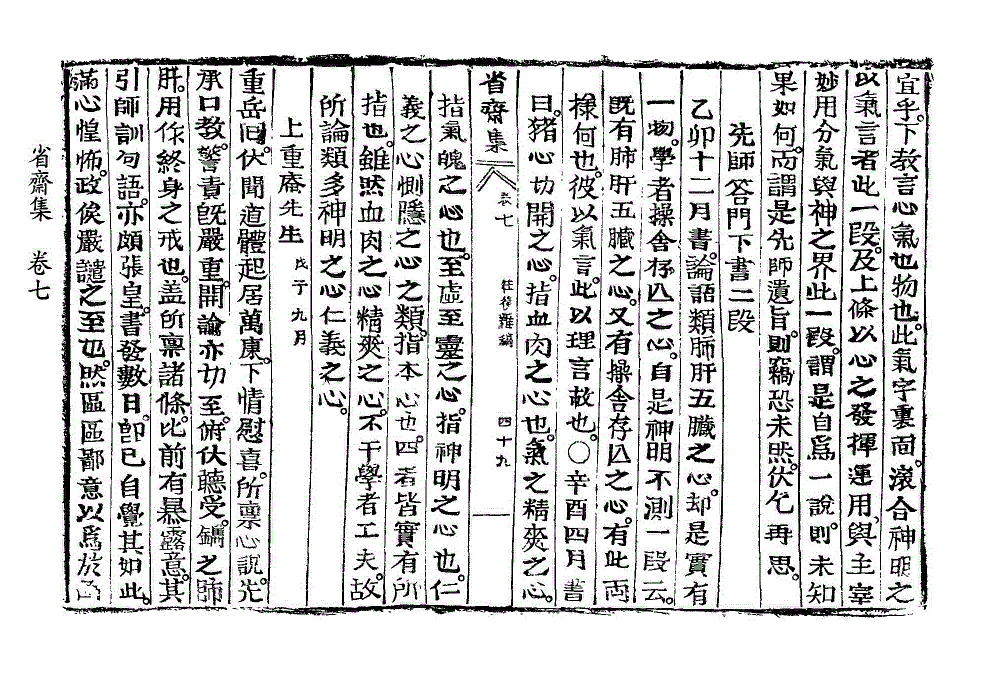 宜乎。下教言心气也物也。此气字里面。滚合神明之以气言者此一段。及上条以心之发挥运用。与主宰妙用分气与神之界此一段。谓是自为一说。则未知果如何。而谓是先师遗旨。则窃恐未然。伏乞再思。
宜乎。下教言心气也物也。此气字里面。滚合神明之以气言者此一段。及上条以心之发挥运用。与主宰妙用分气与神之界此一段。谓是自为一说。则未知果如何。而谓是先师遗旨。则窃恐未然。伏乞再思。先师答门下书二段
乙卯十二月书。论语类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学者操舍存亡之心。自是神明不测一段云。既有肺肝五脏之心。又有操舍存亡之心。有此两㨾何也。彼以气言。此以理言故也。○辛酉四月书曰。猪心切开之心。指血肉之心也。气之精爽之心。指气魄之心也。至虚至灵之心。指神明之心也。仁义之心恻隐之心之类。指本心也。四者皆实有所指也。虽然血肉之心精爽之心。不干学者工夫。故所论类多神明之心仁义之心。
上重庵先生(戊子九月)
重岳回。伏闻道体起居万康。下情慰喜。所禀心说。先承口教。警责既严重。开谕亦切至。俯伏听受。镌之肺肝。用作终身之戒也。盖所禀诸条。比前有暴露意。其引师训句语。亦颇张皇。书发数日。即已自觉其如此。满心惶怖。政俟严谴之至也。然区区鄙意以为于函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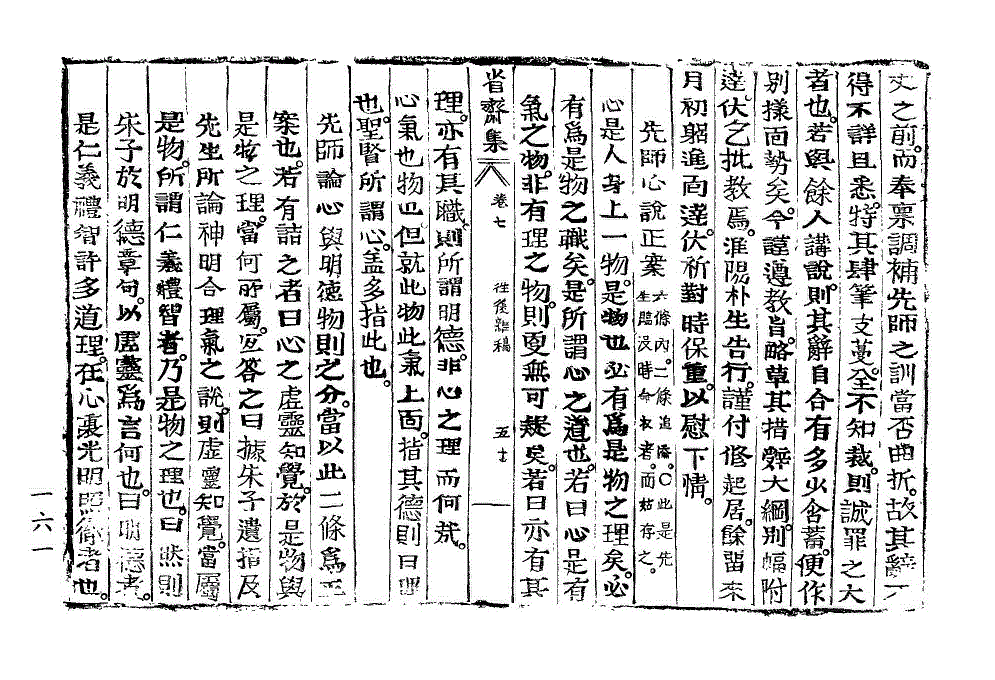 丈之前。而奉禀调补先师之训当否曲折。故其辞不得不详且悉。特其肆笔支蔓。全不知裁。则诚罪之大者也。若与馀人讲说。则其辞自合有多少含蓄。便作别㨾面势矣。今谨遵教旨。略草其措辞大纲。别幅附达。伏乞批教焉。淮阳朴生告行。谨付修起居。馀留来月初躬进面达。伏祈对时保重。以慰下情。
丈之前。而奉禀调补先师之训当否曲折。故其辞不得不详且悉。特其肆笔支蔓。全不知裁。则诚罪之大者也。若与馀人讲说。则其辞自合有多少含蓄。便作别㨾面势矣。今谨遵教旨。略草其措辞大纲。别幅附达。伏乞批教焉。淮阳朴生告行。谨付修起居。馀留来月初躬进面达。伏祈对时保重。以慰下情。先师心说正案(六条内。二条追添。○此是先生临没时命收者。而姑存之。)
心是人身上一物。是物也必有为是物之理矣。必有为是物之职矣。是所谓心之道也。若曰心是有气之物。非有理之物。则更无可疑矣。若曰亦有其理。亦有其职。则所谓明德。非心之理而何哉。
心气也物也。但就此物此气上面。指其德则曰理也。圣贤所谓心。盖多指此也。
先师论心与明德物则之分。当以此二条为正案也。若有诘之者曰心之虚灵知觉。于是物与是物之理。当何所属。宜答之曰据朱子遗指及先生所论神明合理气之说。则虚灵知觉。当属是物。所谓仁义礼智者。乃是物之理也。曰然则朱子于明德章句。以虚灵为言何也。曰明德者。是仁义礼智许多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者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2H 页
 故就是物上。举起虚灵二字。配贴不昧字成文。以形容此德之明尔。非直以虚灵知觉。唤做明德也。曰言圣贤所谓心盖多指此。则其指此物此气而言心者。亦时有之可见。圣贤所指。何故有此两样。曰指此物此气而言心者。依本分辨位正名之辞也。要人见真妄邪正之杂而加省察操存之工也。指是德是理而言心者。就上面推明发挥之辞也。要人见本源真体之正而加准的恢复之工也。言各有当。不可阙一也。
故就是物上。举起虚灵二字。配贴不昧字成文。以形容此德之明尔。非直以虚灵知觉。唤做明德也。曰言圣贤所谓心盖多指此。则其指此物此气而言心者。亦时有之可见。圣贤所指。何故有此两样。曰指此物此气而言心者。依本分辨位正名之辞也。要人见真妄邪正之杂而加省察操存之工也。指是德是理而言心者。就上面推明发挥之辞也。要人见本源真体之正而加准的恢复之工也。言各有当。不可阙一也。心者人之神明。而合理气包动静者也。
心者理与气妙合。而自能神明者也。
先师论心之神明理气名位。当以此二条为正案也。若有诘之者曰神明与虚灵知觉。是一耶二耶。宜答之曰细分则曰神明。曰虚灵。曰知觉。微有所指浅深之差。而断之以名位。则其为理气之合者。未始不一也。其当属物而不得为则者。未始不一也。曰既言理气之合。而犹偏属之物何也。曰凡言合理气者。对单言之理则须属之形而下。且所谓物者。元是理与气合之名也。盖神明灵觉。惟其合理气也。故举其当体则是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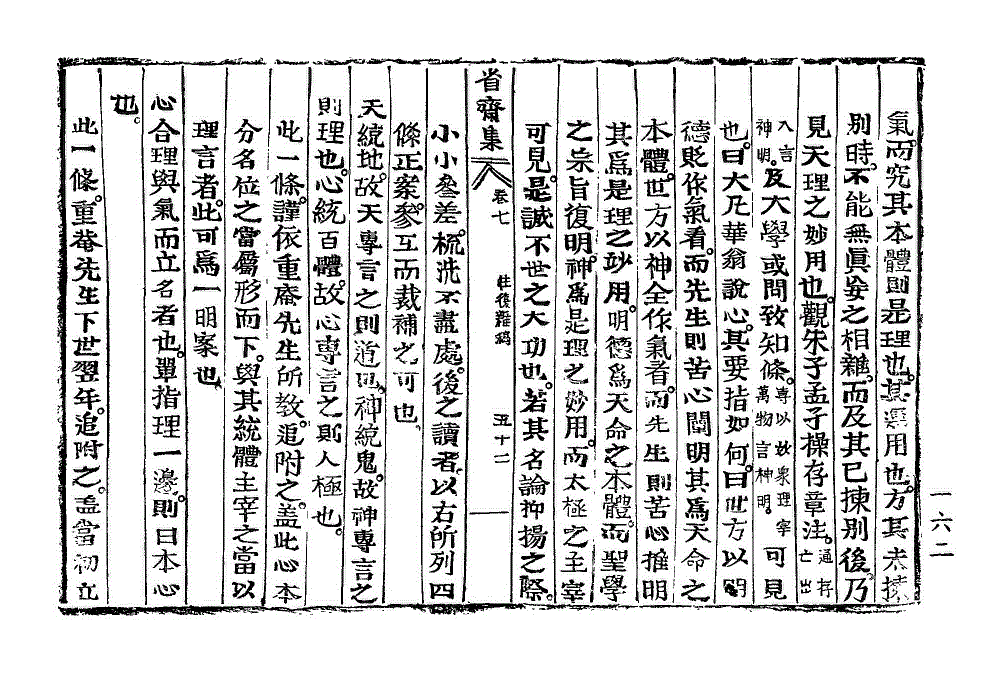 气。而究其本体则是理也。其运用也。方其未拣别时。不能无真妄之相杂。而及其已拣别后。乃见天理之妙用也。观朱子孟子操存章注。(通存亡出入言神明。)及大学或问致知条。(专以妙众理宰万物言神明。)可见也。曰大凡华翁说心。其要指如何。曰世方以明德贬作气看。而先生则苦心阐明其为天命之本体。世方以神全作气看。而先生则苦心推明其为是理之妙用。明德为天命之本体。而圣学之宗旨复明。神为是理之妙用。而太极之主宰可见。是诚不世之大功也。若其名论抑扬之际。小小参差。梳洗不尽处。后之读者。以右所列四条正案。参互而裁补之可也。
气。而究其本体则是理也。其运用也。方其未拣别时。不能无真妄之相杂。而及其已拣别后。乃见天理之妙用也。观朱子孟子操存章注。(通存亡出入言神明。)及大学或问致知条。(专以妙众理宰万物言神明。)可见也。曰大凡华翁说心。其要指如何。曰世方以明德贬作气看。而先生则苦心阐明其为天命之本体。世方以神全作气看。而先生则苦心推明其为是理之妙用。明德为天命之本体。而圣学之宗旨复明。神为是理之妙用。而太极之主宰可见。是诚不世之大功也。若其名论抑扬之际。小小参差。梳洗不尽处。后之读者。以右所列四条正案。参互而裁补之可也。天统地。故天专言之则道也。神统鬼。故神专言之则理也。心统百体。故心专言之则人极也。
此一条。谨依重庵先生所教。追附之。盖此心本分名位之当属形而下。与其统体主宰之当以理言者。此可为一明案也。
心合理与气而立名者也。单指理一边。则曰本心也。
此一条。重庵先生下世翌年。追附之。盖当初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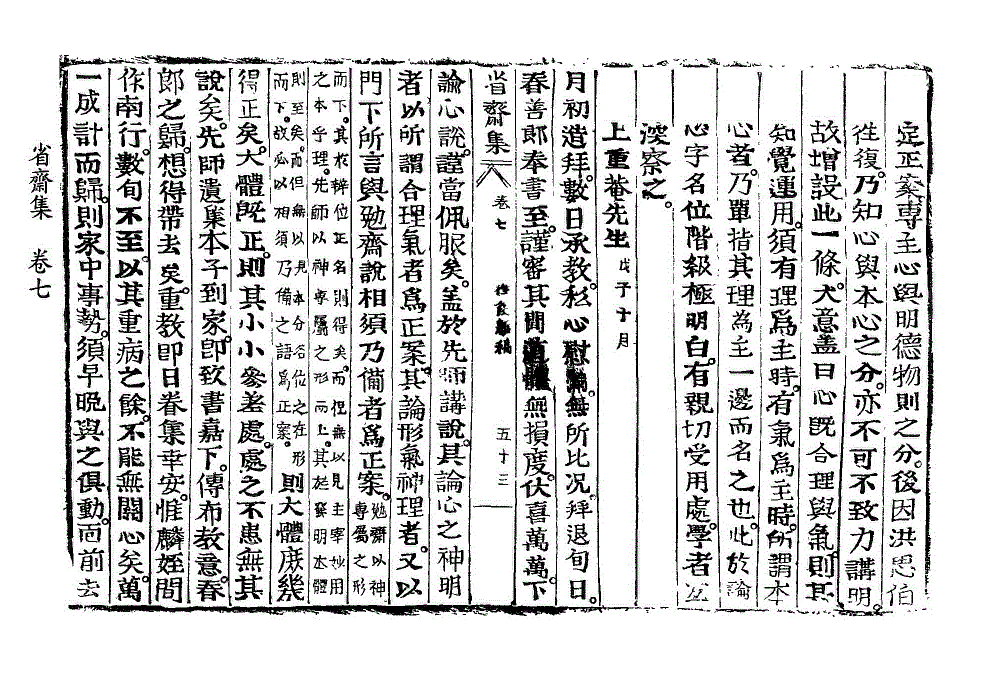 定正案。专主心与明德物则之分。后因洪思伯往复。乃知心与本心之分。亦不可不致力讲明。故增设此一条。大意盖曰心既合理与气。则其知觉运用。须有理为主时。有气为主时。所谓本心者。乃单指其理为主一边而名之也。此于论心字名位阶级极明白。有亲切受用处。学者宜深察之。
定正案。专主心与明德物则之分。后因洪思伯往复。乃知心与本心之分。亦不可不致力讲明。故增设此一条。大意盖曰心既合理与气。则其知觉运用。须有理为主时。有气为主时。所谓本心者。乃单指其理为主一边而名之也。此于论心字名位阶级极明白。有亲切受用处。学者宜深察之。上重庵先生(戊子十月)
月初造拜。数日承教。私心慰满。无所比况。拜退旬日。春善郎奉书至。谨审其间道体无损度。伏喜万万。下谕心说。谨当佩服矣。盖于先师讲说。其论心之神明者以所谓合理气者为正案。其论形气神理者。又以门下所言与勉斋说相须乃备者为正案。(勉斋以神专属之形而下。其于辨位正名则得矣。而但无以见主宰妙用之本乎理。先师以神专属之形而上。其于发明本体则至矣。而但无以见本分名位之在形而下。故必以相须乃备之语为正案。)则大体庶几得正矣。大体既正。则其小小参差处。处之不患无其说矣。先师遗集本子到家。即致书嘉下。传布教意。春郎之归。想得带去矣。重教即日眷集幸安。惟麟侄间作南行。数旬不至。以其重病之馀。不能无关心矣。万一成计而归。则家中事势。须早晚与之俱动。面前去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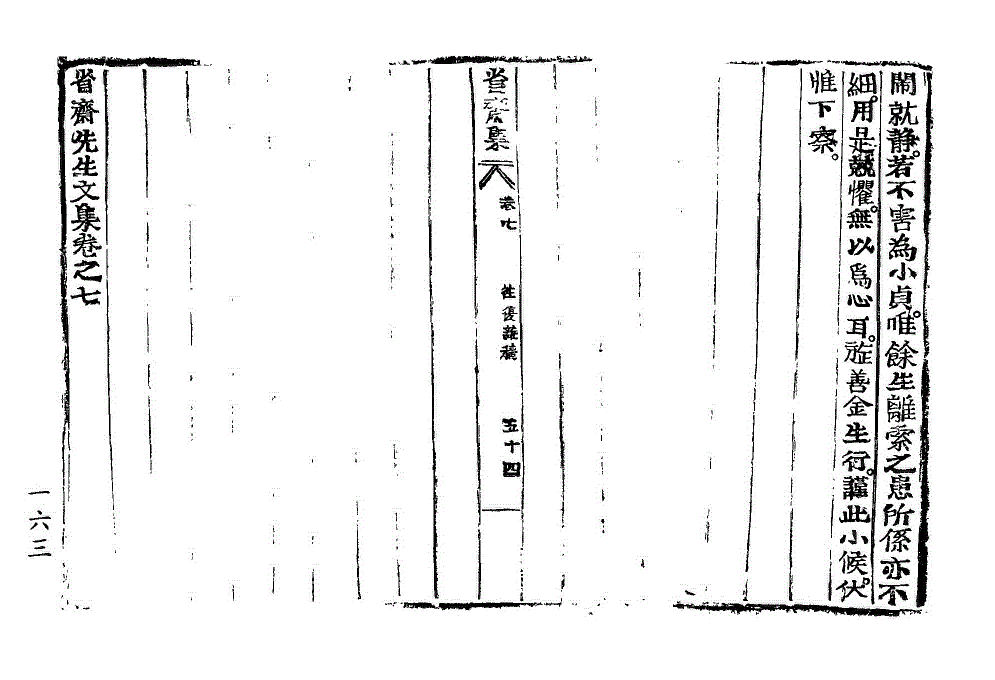 闹就静。若不害为小贞。唯馀生离索之患所系亦不细。用是兢惧。无以为心耳。旌善金生行。谨此小候。伏惟下察。
闹就静。若不害为小贞。唯馀生离索之患所系亦不细。用是兢惧。无以为心耳。旌善金生行。谨此小候。伏惟下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