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往复杂稿
往复杂稿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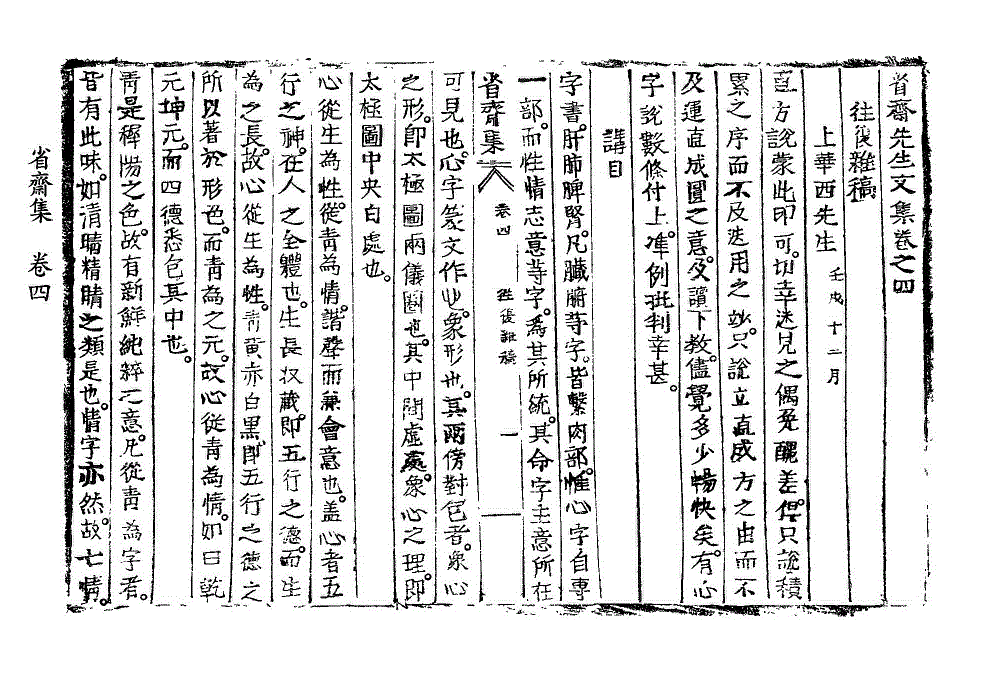 上华西先生(壬戌十二月)
上华西先生(壬戌十二月)直方说蒙此印可。切幸迷见之偶免丑差。但只说积累之序而不及迭用之妙。只说立直成方之由而不及运直成圆之意。及读下教。尽觉多少畅快矣。有心字说数条付上。准例批判幸甚。
讲目
字书。肝肺脾肾。凡脏腑等字。皆系肉部。惟心字自专一部。而性情志意等字。为其所统。其命字主意所在可见也。心字篆文作
心从生为性。从青为情。谐声而兼会意也。盖心者五行之神。在人之全体也。生长收藏。即五行之德。而生为之长。故心从生为性。青黄赤白黑。即五行之德之所以著于形色。而青为之元。故心从青为情。如曰乾元坤元。而四德悉包其中也。
青是稚阳之色。故有新鲜纯粹之意。凡从青为字者。皆有此味。如清晴精睛之类是也。情字亦然。故七情。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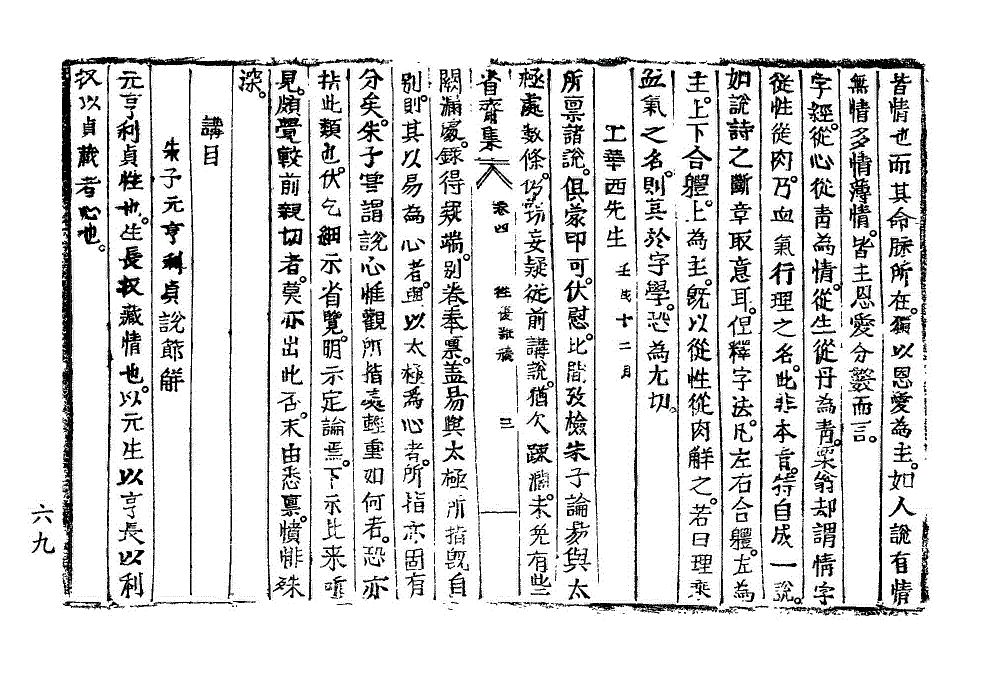 皆情也而其命脉所在。独以恩爱为主。如人说有情无情多情薄情。皆主恩爱分数而言。
皆情也而其命脉所在。独以恩爱为主。如人说有情无情多情薄情。皆主恩爱分数而言。字经。从心从青为情。从生从丹为青。栗翁却谓情字从性从肉。乃血气行理之名。此非本旨。特自成一说。如说诗之断章取意耳。但释字法。凡左右合体。左为主。上下合体。上为主。既以从性从肉解之。若曰理乘血气之名。则其于字学。恐为尤切。
上华西先生(壬戌十二月)
所禀诸说。俱蒙印可。伏慰。比间考检朱子论易与太极处数条。仍窃妄疑从前讲说。犹欠疏阔。未免有些阙漏处。录得疑端。别卷奉禀。盖易与太极所指既自别。则其以易为心者。与以太极为心者。所指亦固有分矣。朱子尝谓说心惟观所指处轻重如何者。恐亦指此类也。伏乞细示省览。明示定论焉。下示比来所见。颇觉较前亲切者。莫亦出此否。末由悉禀。愤悱殊深。
讲目
朱子元亨利贞说节解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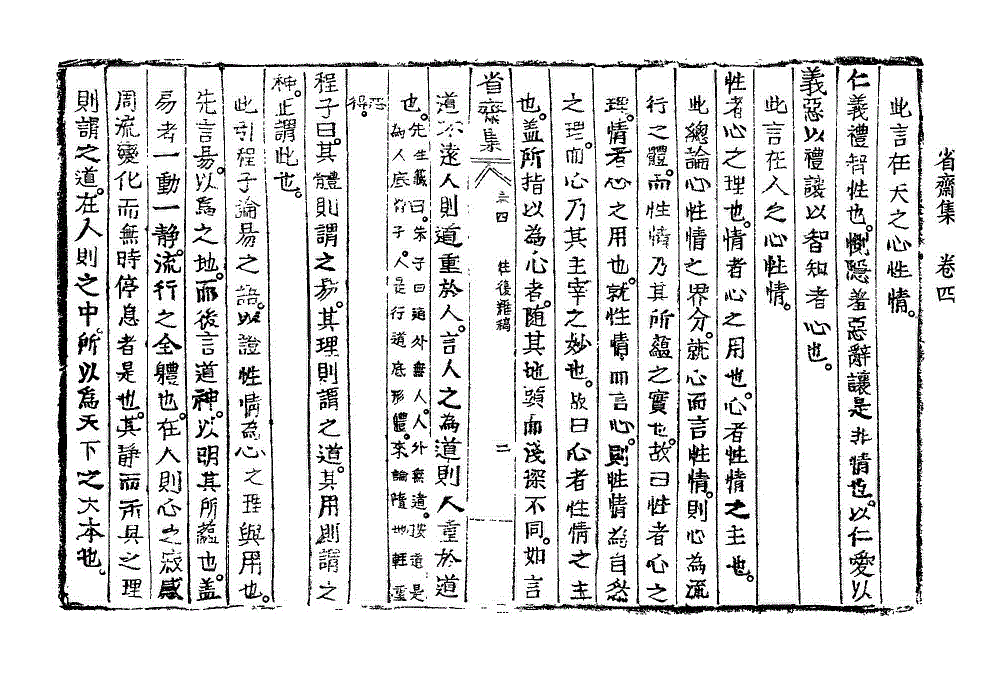 此言在天之心性情。
此言在天之心性情。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
此言在人之心性情。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此总论心性情之界分。就心而言性情。则心为流行之体。而性情乃其所蕴之实也。故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也。就性情而言心。则性情为自然之理。而心乃其主宰之妙也。故曰心者性情之主也。盖所指以为心者。随其地头而浅深不同。如言道不远人则道重于人。言人之为道则人重于道也。(先生签曰。朱子曰道外无人。人外无道。按道是为人底骨子。人是行道底形体。来论随地轻重恐得。)
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
此引程子论易之语。以證性情为心之理与用也。先言易。以为之地。而后言道神。以明其所蕴也。盖易者一动一静。流行之全体也。在人则心之寂感周流变化而无时停息者是也。其静而所具之理则谓之道。在人则之中。所以为天下之大本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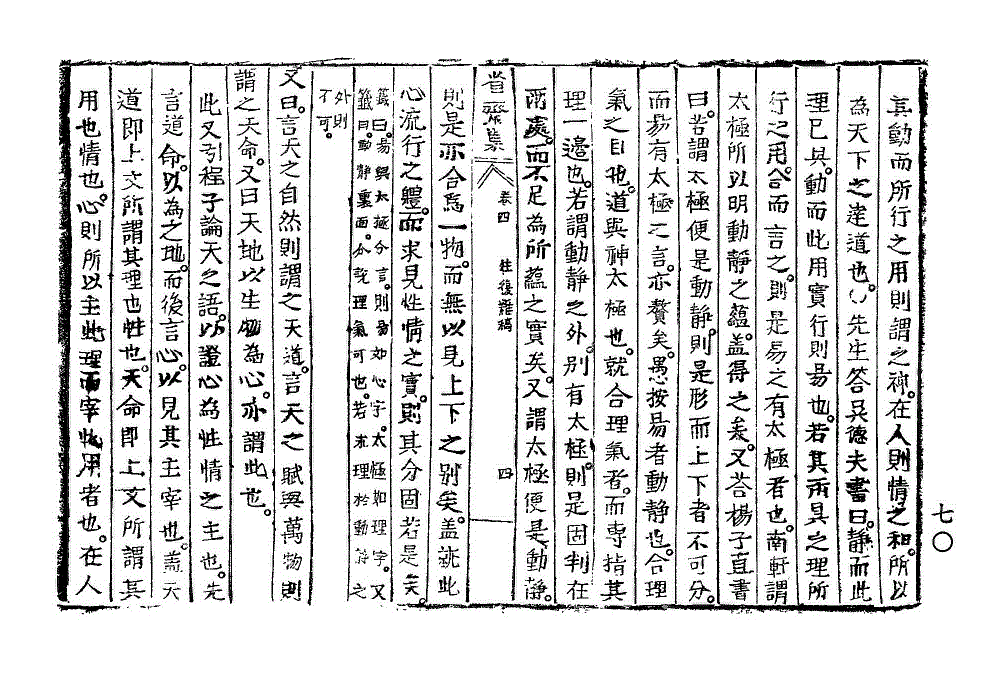 其动而所行之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之和。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先生答吴德夫书曰。静而此理已具。动而此用实行则易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则是易之有太极者也。南轩谓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盖得之矣。又答杨子直书曰。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愚按易者动静也。合理气之目也。道与神太极也。就合理气者。而专指其理一边也。若谓动静之外。别有太极。则是固判在两处。而不足为所蕴之实矣。又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亦合为一物。而无以见上下之别矣。盖就此心流行之体。而求见性情之实。则其分固若是矣。(签曰。易与太极分言。则易如心字。太极如理字。又签曰。动静里面。分说理气可也。若求理于动静之外则不可。)
其动而所行之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之和。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先生答吴德夫书曰。静而此理已具。动而此用实行则易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则是易之有太极者也。南轩谓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盖得之矣。又答杨子直书曰。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愚按易者动静也。合理气之目也。道与神太极也。就合理气者。而专指其理一边也。若谓动静之外。别有太极。则是固判在两处。而不足为所蕴之实矣。又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亦合为一物。而无以见上下之别矣。盖就此心流行之体。而求见性情之实。则其分固若是矣。(签曰。易与太极分言。则易如心字。太极如理字。又签曰。动静里面。分说理气可也。若求理于动静之外则不可。)又曰。言天之自然则谓之天道。言天之赋与万物则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
此又引程子论天之语。以證心为性情之主也。先言道命。以为之地。而后言心。以见其主宰也。盖天道即上文所谓其理也性也。天命即上文所谓其用也情也。心则所以主此理而宰此用者也。在人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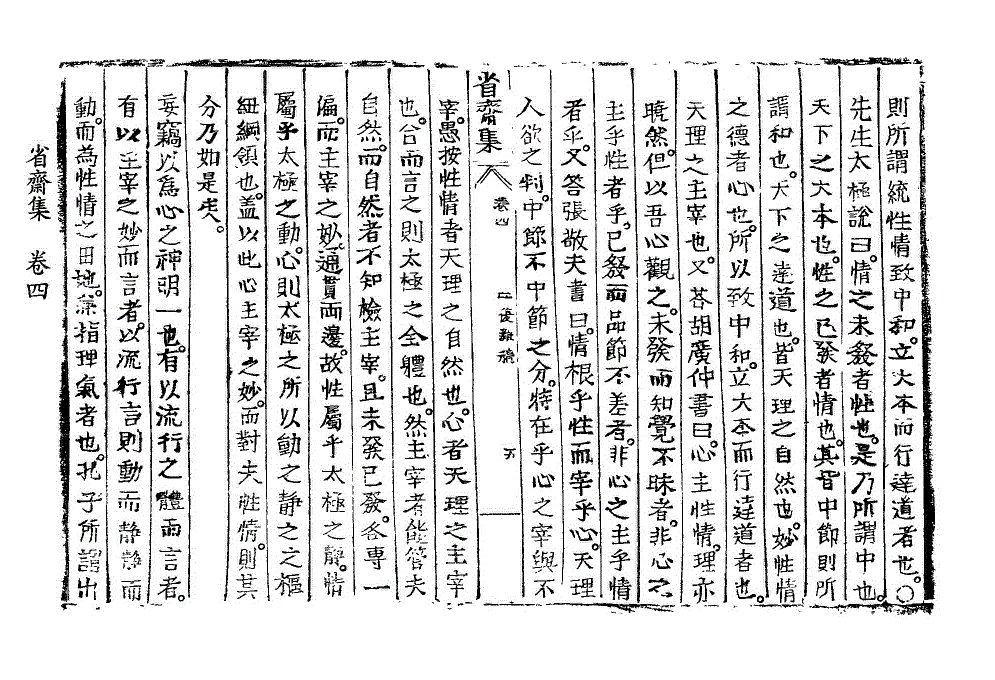 则所谓统性情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先生太极说曰。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又答胡广仲书曰。心主性情。理亦晓然。但以吾心观之。未发而知觉不昧者。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发而品节不差者。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又答张敬夫书曰。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天理人欲之判。中节不中节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愚按性情者天理之自然也。心者天理之主宰也。合而言之则太极之全体也。然主宰者能管夫自然。而自然者不知检主宰。且未发已发。各专一偏。而主宰之妙。通贯两边。故性属乎太极之静。情属乎太极之动。心则太极之所以动之静之之枢纽纲领也。盖以此心主宰之妙。而对夫性情。则其分乃如是矣。
则所谓统性情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先生太极说曰。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又答胡广仲书曰。心主性情。理亦晓然。但以吾心观之。未发而知觉不昧者。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发而品节不差者。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又答张敬夫书曰。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天理人欲之判。中节不中节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愚按性情者天理之自然也。心者天理之主宰也。合而言之则太极之全体也。然主宰者能管夫自然。而自然者不知检主宰。且未发已发。各专一偏。而主宰之妙。通贯两边。故性属乎太极之静。情属乎太极之动。心则太极之所以动之静之之枢纽纲领也。盖以此心主宰之妙。而对夫性情。则其分乃如是矣。妄窃以为心之神明一也。有以流行之体而言者。有以主宰之妙而言者。以流行言则动而静静而动。而为性情之田地。兼指理气者也。孔子所谓出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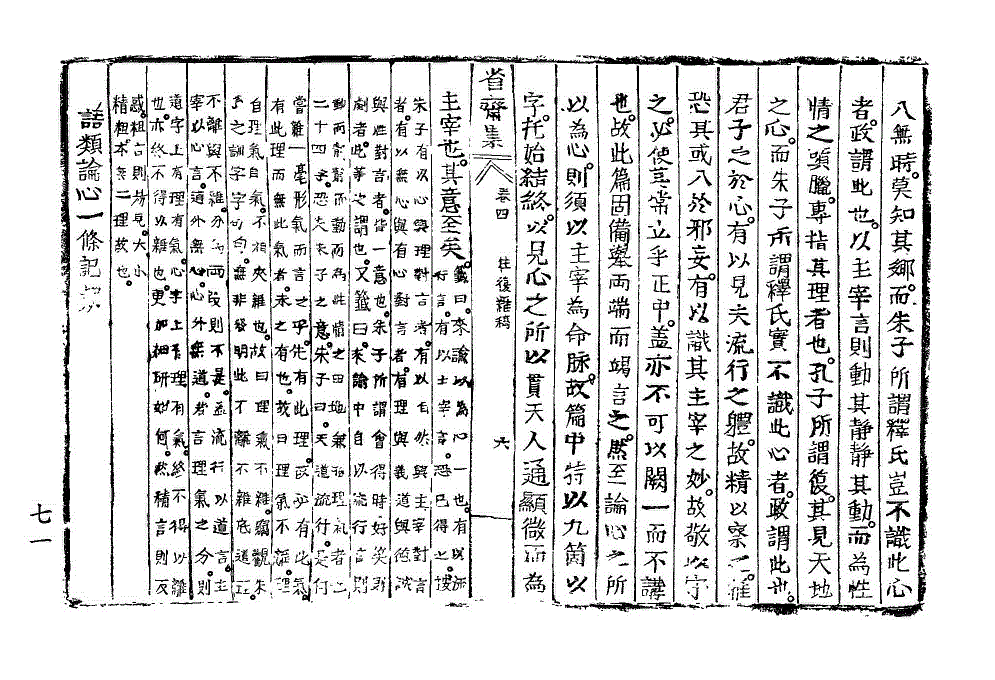 入无时。莫知其乡。而朱子所谓释氏岂不识此心者。政谓此也。以主宰言则动其静静其动。而为性情之头腊。专指其理者也。孔子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而朱子所谓释氏实不识此心者。政谓此也。君子之于心。有以见夫流行之体。故精以察之。惟恐其或入于邪妄。有以识其主宰之妙。故敬以守之。必使其常立乎正中。盖亦不可以阙一而不讲也。故此篇固备举两端而竭言之。然至论心之所以为心。则须以主宰为命脉。故篇中特以九个以字。托始结终。以见心之所以贯天人通显微而为主宰也。其意至矣。签曰。来谕以为心一也。有以流行言。有以士(一作主)宰言。恐已得之。按朱子有以心与理对言者。有以自然与主宰对言者。有以无心与有心对言者。有理与义道与德诚与性对言者。皆一意也。朱子所谓会得时好笑则剧者。此等之谓也。又签曰。来谕中自以流行言则动而静静而动而为性情之田地兼指理气者之二十四字。恐失朱子之意。朱子曰。天道流行。是何尝杂一毫形气而言之乎。先有此理。故必有此气。有此理而无此气者。未之有也。故曰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也。故曰理气不杂。窃观朱子之训字字句句。无非发明此不离不杂底道理。不离与不杂。分为两段则不是。盖流行以道言。主宰以心言。道外无心。心外无道。若言理气之分。则道字上有理有气。心字上有理有气。终不得以离也。亦终不得以杂也。更加细研如何。然精言则反惑。粗言则易见。大小精粗。本无二理故也。
入无时。莫知其乡。而朱子所谓释氏岂不识此心者。政谓此也。以主宰言则动其静静其动。而为性情之头腊。专指其理者也。孔子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而朱子所谓释氏实不识此心者。政谓此也。君子之于心。有以见夫流行之体。故精以察之。惟恐其或入于邪妄。有以识其主宰之妙。故敬以守之。必使其常立乎正中。盖亦不可以阙一而不讲也。故此篇固备举两端而竭言之。然至论心之所以为心。则须以主宰为命脉。故篇中特以九个以字。托始结终。以见心之所以贯天人通显微而为主宰也。其意至矣。签曰。来谕以为心一也。有以流行言。有以士(一作主)宰言。恐已得之。按朱子有以心与理对言者。有以自然与主宰对言者。有以无心与有心对言者。有理与义道与德诚与性对言者。皆一意也。朱子所谓会得时好笑则剧者。此等之谓也。又签曰。来谕中自以流行言则动而静静而动而为性情之田地兼指理气者之二十四字。恐失朱子之意。朱子曰。天道流行。是何尝杂一毫形气而言之乎。先有此理。故必有此气。有此理而无此气者。未之有也。故曰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也。故曰理气不杂。窃观朱子之训字字句句。无非发明此不离不杂底道理。不离与不杂。分为两段则不是。盖流行以道言。主宰以心言。道外无心。心外无道。若言理气之分。则道字上有理有气。心字上有理有气。终不得以离也。亦终不得以杂也。更加细研如何。然精言则反惑。粗言则易见。大小精粗。本无二理故也。语类论心一条记疑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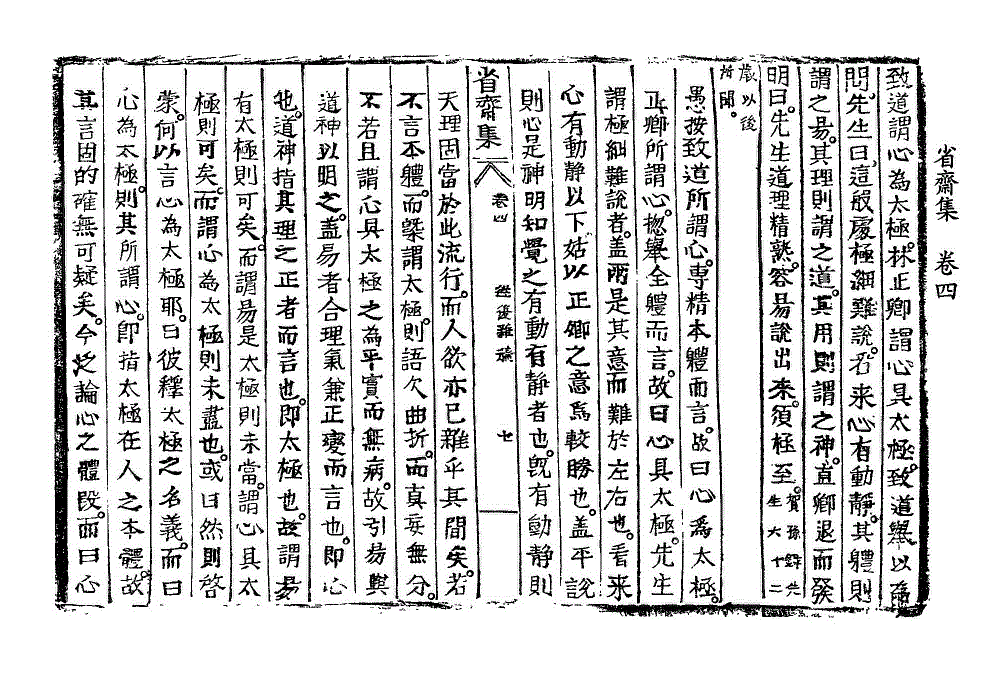 致道谓心为太极。林正卿谓心具太极。致道举以为问。先生曰。这般处极细难说。看来心有动静。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直卿退而发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说出来。须极至。(贺孙录先生六十二岁以后所闻。)
致道谓心为太极。林正卿谓心具太极。致道举以为问。先生曰。这般处极细难说。看来心有动静。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直卿退而发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说出来。须极至。(贺孙录先生六十二岁以后所闻。)愚按致道所谓心。专精本体而言。故曰心为太极。正卿所谓心。揔举全体而言。故曰心具太极。先生谓极细难说者。盖两是其意而难于左右也。看来心有动静以下。姑以正卿之意为较胜也。盖平说则心是神明知觉之有动有静者也。既有动静则天理固当于此流行。而人欲亦已杂乎其间矣。若不言本体。而槩谓太极。则语欠曲折。而真妄无分。不若且谓心具太极之为平实而无病。故引易与道神以明之。盖易者合理气兼正变而言也。即心也。道神指其理之正者而言也。即太极也。故谓易有太极则可矣。而谓易是太极则未当。谓心具太极则可矣。而谓心为太极则未尽也。或曰然则启蒙。何以言心为太极耶。曰彼释太极之名义。而曰心为太极。则其所谓心。即指太极在人之本体。故其言固的确无可疑矣。今泛论心之体段。而曰心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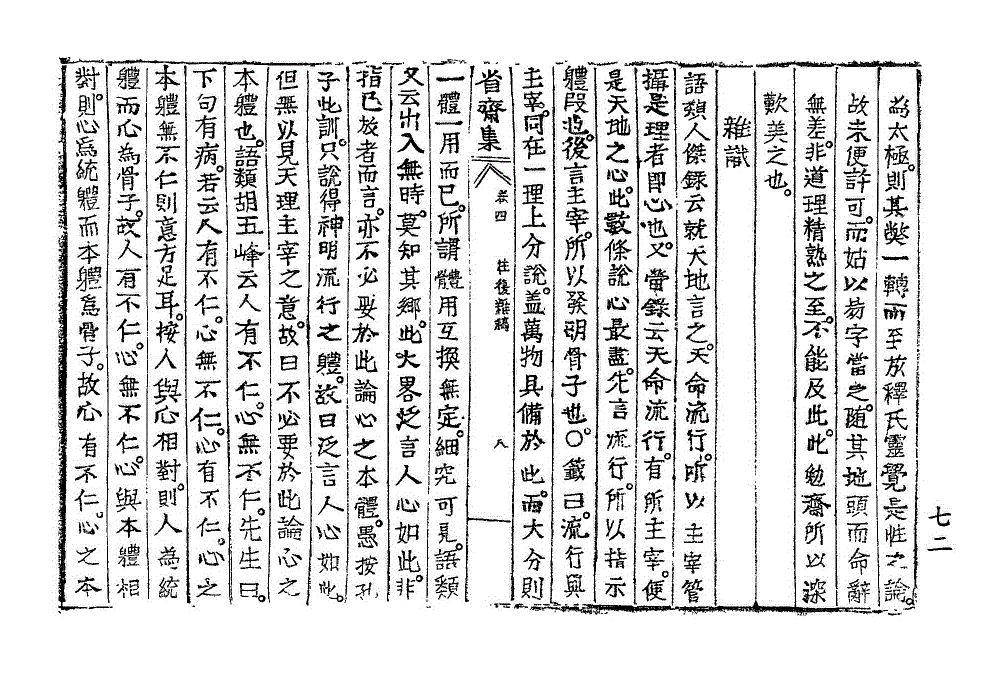 为太极。则其弊一转而至于释氏灵觉是性之论。故未便许可。而姑以易字当之。随其地头而命辞无差。非道理精熟之至。不能及此。此勉斋所以深叹美之也。
为太极。则其弊一转而至于释氏灵觉是性之论。故未便许可。而姑以易字当之。随其地头而命辞无差。非道理精熟之至。不能及此。此勉斋所以深叹美之也。杂识
语类人杰录云就天地言之。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心也。又㽦录云天命流行。有所主宰。便是天地之心。此数条说心最尽。先言流行。所以指示体段也。后言主宰。所以发明骨子也。○签曰。流行与主宰。同在一理上分说。盖万物具备于此。而大分则一体一用而已。所谓体用互换无定。细究可见。语类又云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大略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论心之本体。愚按孔子此训。只说得神明流行之体。故曰泛言人心如此。但无以见天理主宰之意。故曰不必要于此论心之本体也。语类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先生曰。下句有病。若云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则意方足耳。按人与心相对。则人为统体而心为骨子。故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心与本体相对。则心为统体而本体为骨子。故心有不仁。心之本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体无不仁。盖随其所指而泛切不同也。○签曰。朱子修润胡五峰之言。其义以为人则一也。有仁与不仁之异者。由于气禀也。而其所得于天之心。又未尝不同。论厥初则赤子之心。何尝不善。但心有尽与不尽存与不存之异。然论其本心。则又未尝不同也。本心即指仁义之心。恻隐羞恶之心也。如此解释。似尤端的。未知何如。
体无不仁。盖随其所指而泛切不同也。○签曰。朱子修润胡五峰之言。其义以为人则一也。有仁与不仁之异者。由于气禀也。而其所得于天之心。又未尝不同。论厥初则赤子之心。何尝不善。但心有尽与不尽存与不存之异。然论其本心。则又未尝不同也。本心即指仁义之心。恻隐羞恶之心也。如此解释。似尤端的。未知何如。性是心之理。理在心为性。此等心字泛阔。即中庸序上文所谓心一而已矣之心也。心是性情之主。心统性情。此等心字端的。即中庸序下文所谓守其本心之正之心也。
心以流行而对性情。则心为阴阳变化之体。而性情为太极体用之实。以主宰而对性情。则性情为阴静阳动之象。而为太极枢纽之妙。
心统性情。统字有兼该之意。有主宰之意。孟子指性而言曰仁义之心。指情而言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此两训皆所以明心之兼该性情。而其于主宰之意则少欠发挥。故朱子论心统性情之语曰。孟子说心许多。皆未有似此语端的。又曰。二程却无一句似此切。○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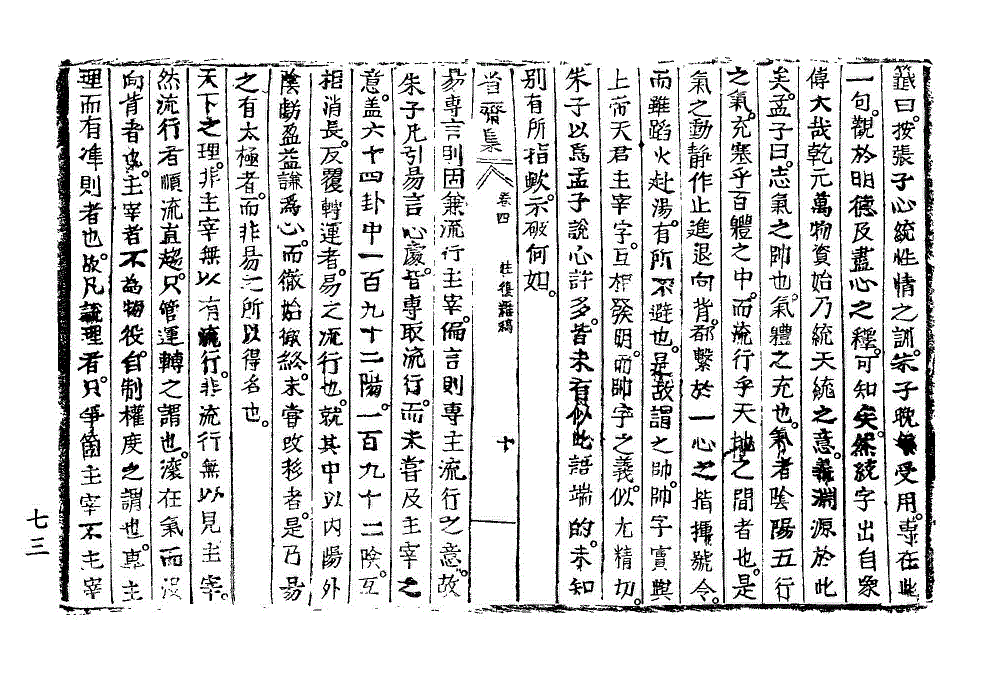 签曰。按张子心统性情之训。朱子晚年受用。专在此一句。观于明德及尽心之释。可知矣。然统字出自象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统之意。义渊源于此矣。孟子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者阴阳五行之气。充塞乎百体之中。而流行乎天地之间者也。是气之动静作止进退向背。都系于一心之指挥号令。而虽蹈火赴汤。有所不避也。是故谓之帅。帅字实与上帝天君主宰字。互相发明。而帅字之义。似尤精切。朱子以为孟子说心许多。皆未有似此语端的。未知别有所指欤。示破何如。
签曰。按张子心统性情之训。朱子晚年受用。专在此一句。观于明德及尽心之释。可知矣。然统字出自象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统之意。义渊源于此矣。孟子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者阴阳五行之气。充塞乎百体之中。而流行乎天地之间者也。是气之动静作止进退向背。都系于一心之指挥号令。而虽蹈火赴汤。有所不避也。是故谓之帅。帅字实与上帝天君主宰字。互相发明。而帅字之义。似尤精切。朱子以为孟子说心许多。皆未有似此语端的。未知别有所指欤。示破何如。易专言则固兼流行主宰。偏言则专主流行之意。故朱子凡引易言心处。皆专取流行。而未尝及主宰之意。盖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阳。一百九十二阴。互相消长。反覆转运者。易之流行也。就其中以内阳外阴亏盈益谦为心。而彻始彻终。未尝改移者。是乃易之有太极者。而非易之所以得名也。
天下之理。非主宰无以有流行。非流行无以见主宰。然流行者顺流直趋。只管运转之谓也。滚在气而没向背者也。主宰者不为物役。自制权度之谓也。专主理而有准则者也。故凡说理者。只争个主宰不主宰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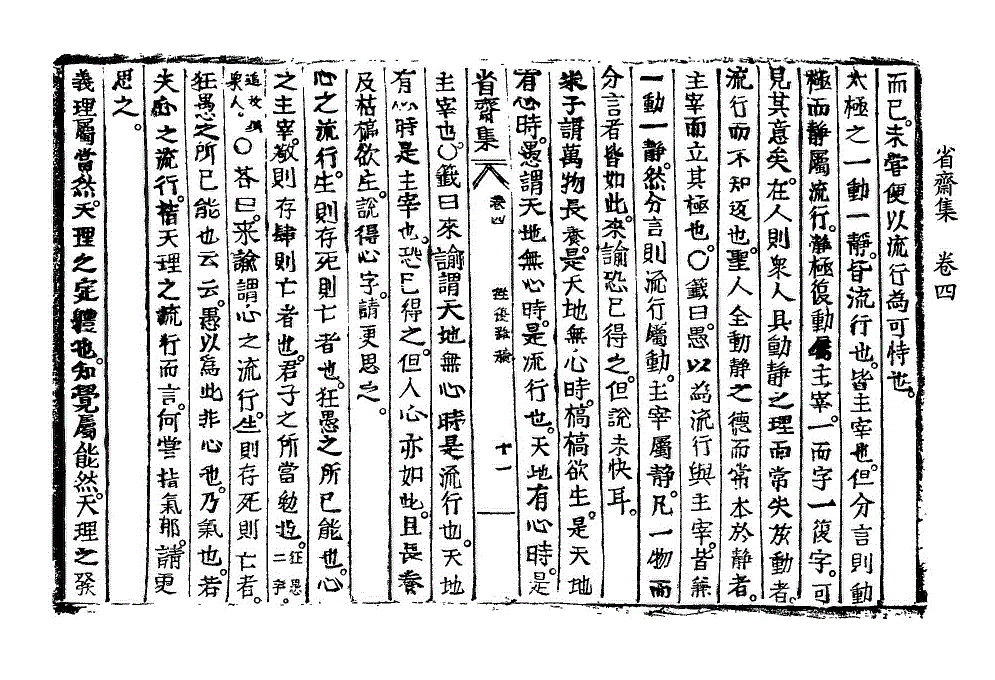 而已。未尝便以流行为可恃也。
而已。未尝便以流行为可恃也。太极之一动一静。皆流行也。皆主宰也。但分言则动极而静属流行。静极复动属主宰。一而字一复字。可见其意矣。在人则众人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于动者。流行而不知返也。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于静者。主宰而立其极也。○签曰。愚以为流行与主宰。皆兼一动一静。然分言则流行属动。主宰属静。凡一物而分言者皆如此。来谕恐已得之。但说未快耳。
朱子谓万物长养。是天地无心时。槁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时。愚谓天地无心时。是流行也。天地有心时。是主宰也。○签曰来谕谓天地无心时是流行也。天地有心时是主宰也。恐已得之。但人心亦如此。且长养及枯槁欲生。说得心字。请更思之。
心之流行。生则存死则亡者也。狂愚之所已能也。心之主宰。敬则存肆则亡者也。君子之所当勉也。(狂愚二字。追放以众人。)○答曰。来谕谓心之流行。生则存死则亡者。狂愚之所已能也云云。愚以为此非心也。乃气也。若夫心之流行。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何尝指气耶。请更思之。
义理属当然。天理之定体也。知觉属能然。天理之发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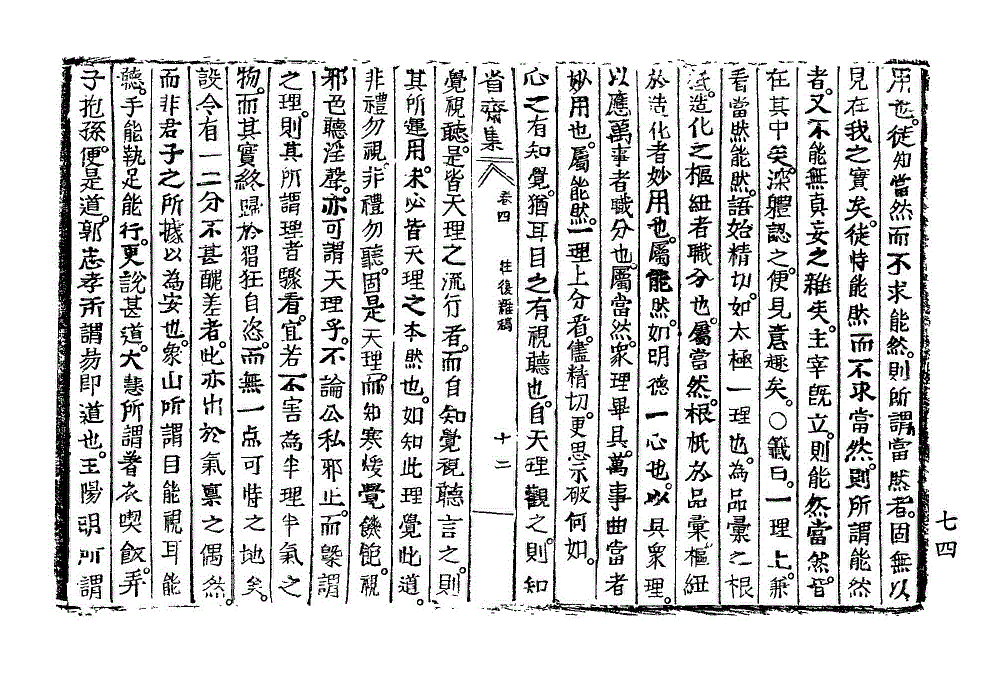 用也。徒知当然而不求能然。则所谓当然者。固无以见在我之实矣。徒恃能然而不求当然。则所谓能然者。又不能无真妄之杂矣。主宰既立。则能然当然。皆在其中矣。深体认之。便见意趣矣。○签曰。一理上。兼看当然能然。语始精切。如太极一理也。为品汇之根柢。造化之枢纽者职分也。属当然。根柢于品汇。枢纽于造化者妙用也。属能然。如明德一心也。以具众理。以应万事者职分也。属当然。众理毕具。万事曲当者妙用也。属能然。一理上分看。尽精切。更思示破何如。
用也。徒知当然而不求能然。则所谓当然者。固无以见在我之实矣。徒恃能然而不求当然。则所谓能然者。又不能无真妄之杂矣。主宰既立。则能然当然。皆在其中矣。深体认之。便见意趣矣。○签曰。一理上。兼看当然能然。语始精切。如太极一理也。为品汇之根柢。造化之枢纽者职分也。属当然。根柢于品汇。枢纽于造化者妙用也。属能然。如明德一心也。以具众理。以应万事者职分也。属当然。众理毕具。万事曲当者妙用也。属能然。一理上分看。尽精切。更思示破何如。心之有知觉。犹耳目之有视听也。自天理观之。则知觉视听。是皆天理之流行者。而自知觉视听言之。则其所运用。未必皆天理之本然也。如知此理觉此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固是天理。而知寒煖觉饥饱。视邪色听淫声。亦可谓天理乎。不论公私邪正。而槩谓之理。则其所谓理者骤看。宜若不害为半理半气之物。而其实终归于猖狂自恣。而无一点可恃之地矣。设令有一二分不甚丑差者。此亦出于气禀之偶然。而非君子之所据以为安也。象山所谓目能视耳能听。手能执足能行。更说甚道。大慧所谓着衣吃饭。弄子抱孙。便是道。郭志孝所谓易即道也。王阳明所谓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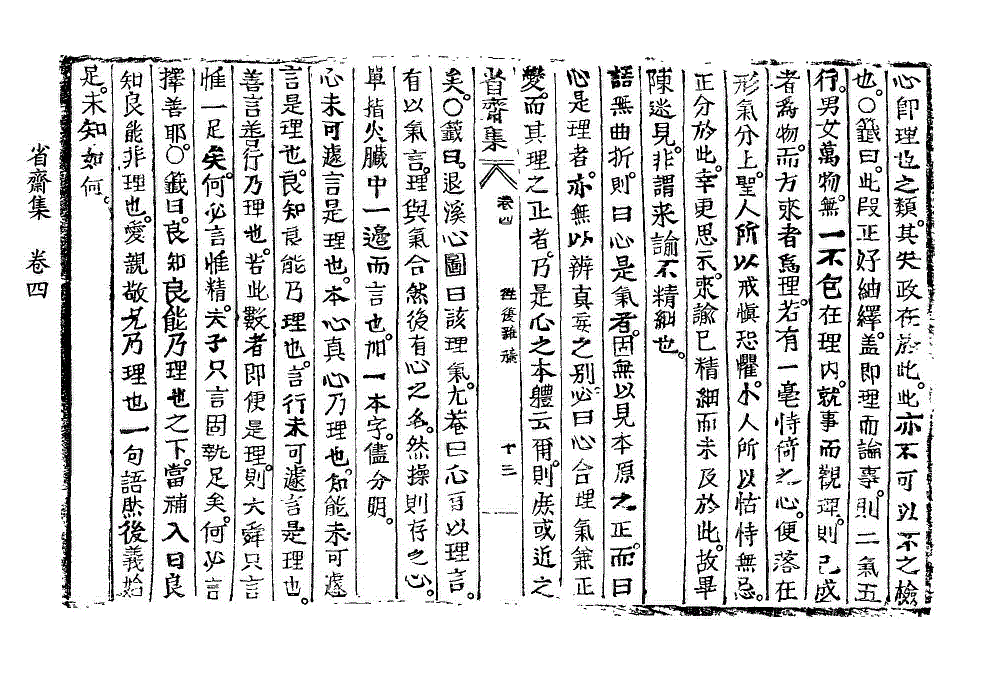 心即理也之类。其失政在于此。此亦不可以不之检也。○签曰。此段正好䌷绎。盖即理而论事。则二气五行男女万物。无一不包在理内。就事而观理。则已成者为物。而方来者为理。若有一毫恃倚之心。便落在形气分上。圣人所以戒慎恐惧。小人所以怙恃无忌。正分于此。幸更思示。来谕已精细而未及于此。故毕陈迷见。非谓来谕不精细也。
心即理也之类。其失政在于此。此亦不可以不之检也。○签曰。此段正好䌷绎。盖即理而论事。则二气五行男女万物。无一不包在理内。就事而观理。则已成者为物。而方来者为理。若有一毫恃倚之心。便落在形气分上。圣人所以戒慎恐惧。小人所以怙恃无忌。正分于此。幸更思示。来谕已精细而未及于此。故毕陈迷见。非谓来谕不精细也。语无曲折。则曰心是气者。固无以见本原之正。而曰心是理者。亦无以辨真妄之别。必曰心合理气兼正变。而其理之正者。乃是心之本体云尔。则庶或近之矣。○签曰。退溪心图曰该理气。尤庵曰心有以理言。有以气言。理与气合然后有心之名。然操则存之心。单指火脏中一边而言也。加一本字。尽分明。
心未可遽言是理也。本心真心乃理也。知能未可遽言是理也。良知良能乃理也。言行未可遽言是理也。善言善行乃理也。若此数者即便是理。则大舜只言惟一足矣。何必言惟精。夫子只言固执足矣。何必言择善耶。○签曰。良知良能乃理也之下。当补入曰良知良能非理也。爱亲敬兄乃理也一句语然后义始足。未知如何。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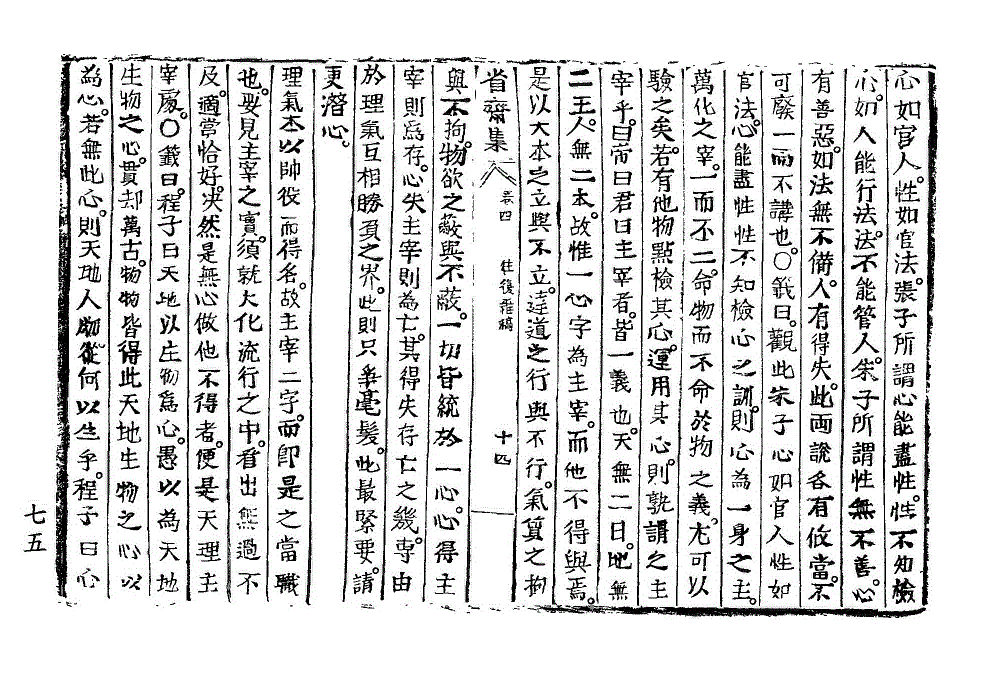 心如官人。性如官法。张子所谓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如人能行法。法不能管人。朱子所谓性无不善。心有善恶。如法无不备。人有得失。此两说各有攸当。不可废一而不讲也。○签曰。观此朱子心如官人性如官法。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之训。则心为一身之主。万化之宰。一而不二。命物而不命于物之义。尤可以验之矣。若有他物点检其心。运用其心。则孰谓之主宰乎。曰帝曰君曰主宰者。皆一义也。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人无二本。故惟一心字为主宰。而他不得与焉。是以大本之立与不立。达道之行与不行。气质之拘与不拘。物欲之蔽与不蔽。一切皆统于一心。心得主宰则为存。心失主宰则为亡。其得失存亡之几。专由于理气互相胜负之界。此则只争毫发。此最紧要。请更潜心。
心如官人。性如官法。张子所谓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如人能行法。法不能管人。朱子所谓性无不善。心有善恶。如法无不备。人有得失。此两说各有攸当。不可废一而不讲也。○签曰。观此朱子心如官人性如官法。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之训。则心为一身之主。万化之宰。一而不二。命物而不命于物之义。尤可以验之矣。若有他物点检其心。运用其心。则孰谓之主宰乎。曰帝曰君曰主宰者。皆一义也。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人无二本。故惟一心字为主宰。而他不得与焉。是以大本之立与不立。达道之行与不行。气质之拘与不拘。物欲之蔽与不蔽。一切皆统于一心。心得主宰则为存。心失主宰则为亡。其得失存亡之几。专由于理气互相胜负之界。此则只争毫发。此最紧要。请更潜心。理气本以帅役而得名。故主宰二字。而即是之当职也。要见主宰之实。须就大化流行之中。看出无过不及。适当恰好。决然是无心做他不得者。便是天理主宰处。○签曰。程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愚以为天地生物之心。贯却万古。物物皆得此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若无此心。则天地人物。从何以生乎。程子曰心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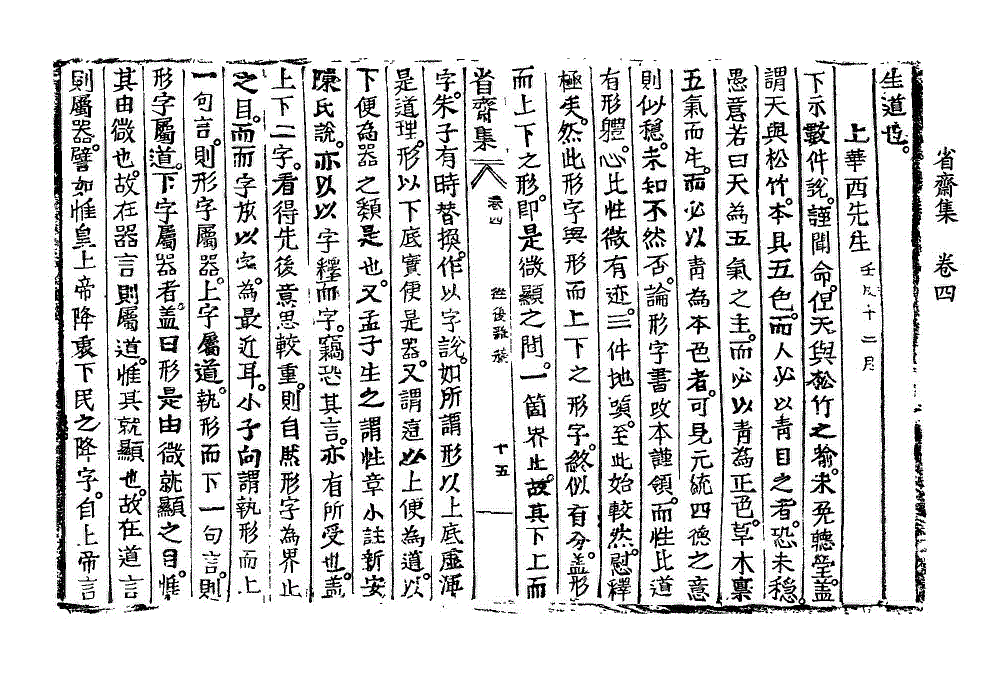 生道也。
生道也。上华西先生(壬戌十二月)
下示数件说。谨闻命。但天与松竹之喻。未免听莹。盖谓天与松竹。本具五色。而人必以青目之者。恐未稳。愚意若曰天为五气之主。而必以青为正色。草木禀五气而生。而必以青为本色者。可见元统四德之意则似稳。未知不然否。论形字书改本谨领。而性比道有形体。心比性微有迹。三件地头。至此始较然。慰释极矣。然此形字与形而上下之形字。终似有分。盖形而上下之形。即是微显之间。一个界止。故其下上而字。朱子有时替换。作以字说。如所谓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以下底实便是器。又谓这以上便为道。以下便为器之类是也。又孟子生之谓性章小注新安陈氏说。亦以以字释而字。窃恐其言。亦有所受也。盖上下二字。看得先后意思较重。则自然形字为界止之目。而而字于以字。为最近耳。小子向谓执形而上一句言。则形字属器。上字属道。执形而下一句言。则形字属道。下字属器者。盖曰形是由微就显之目。惟其由微也。故在器言则属道。惟其就显也。故在道言则属器。譬如惟皇上帝降衷下民之降字。自上帝言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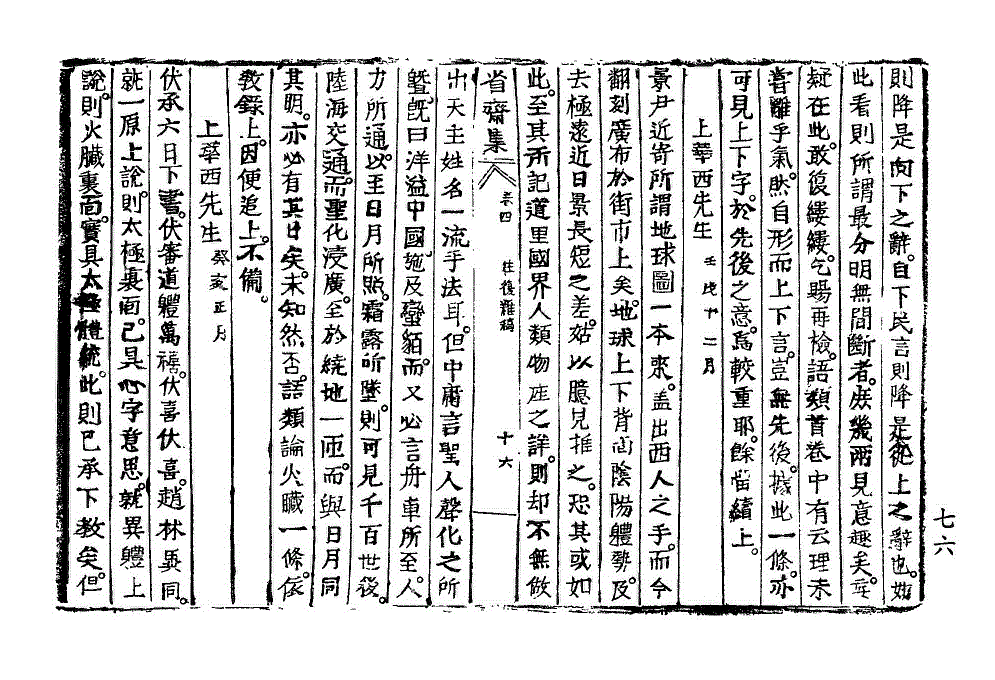 则降是向下之辞。自下民言则降是从上之辞也。如此看则所谓最分明无间断者。庶几两见意趣矣。妄疑在此。敢复缕缕。乞赐再检。语类首卷中有云理未尝离乎气。然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据此一条。亦可见上下字。于先后之意。为较重耶。馀留续上。
则降是向下之辞。自下民言则降是从上之辞也。如此看则所谓最分明无间断者。庶几两见意趣矣。妄疑在此。敢复缕缕。乞赐再检。语类首卷中有云理未尝离乎气。然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据此一条。亦可见上下字。于先后之意。为较重耶。馀留续上。上华西先生(壬戌十二月)
景尹近寄所谓地球图一本来。盖出西人之手。而今翻刻广布于街市上矣。地球上下背面阴阳体势。及去极远近日景长短之差。姑以臆见推之。恐其或如此。至其所记道里国界人类物产之详。则却不无做出天主姓名一流手法耳。但中庸言圣人声化之所暨。既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而又必言舟车所至。人力所通。以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则可见千百世后。陆海交通。而圣化浸广。至于绕地一匝。而与日月同其明。亦必有其日矣。未知然否。语类论火脏一条。依教录上。因便追上。不备。
上华西先生(癸亥正月)
伏承六日下书。伏审道体万禧。伏喜伏喜。赵林异同。就一原上说。则太极里面。已具心字意思。就异体上说。则火脏里面。实具太极体统。此则已承下教矣。但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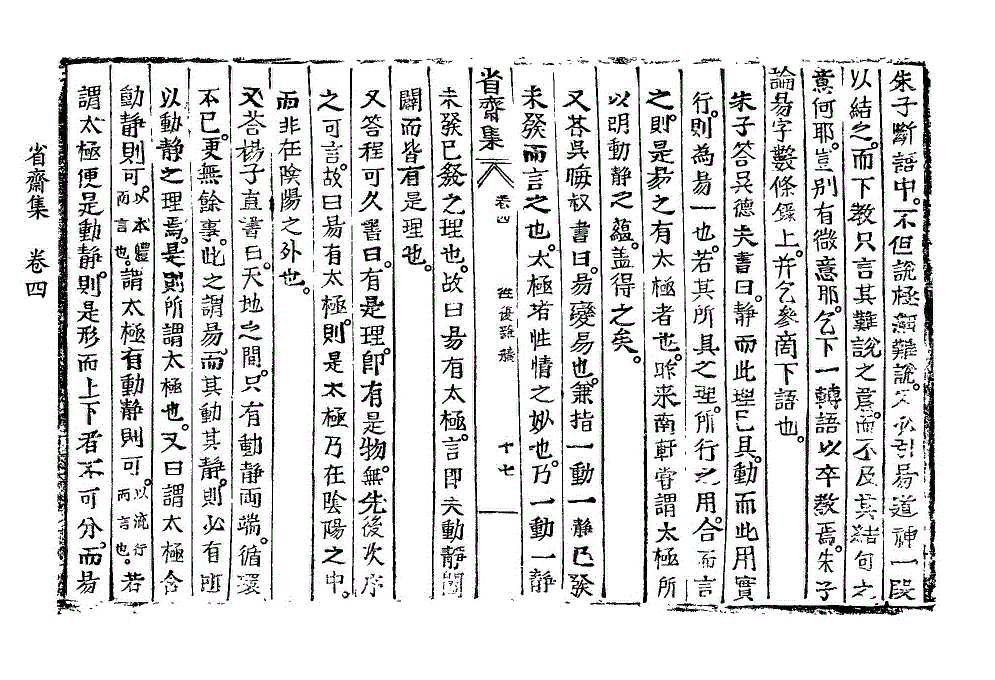 朱子断语中。不但说极细难说。又必引易道神一段以结之。而下教只言其难说之意。而不及其结句之意何耶。岂别有微意耶。乞下一转语以卒教焉。朱子论易字数条录上。并乞参商下语也。
朱子断语中。不但说极细难说。又必引易道神一段以结之。而下教只言其难说之意。而不及其结句之意何耶。岂别有微意耶。乞下一转语以卒教焉。朱子论易字数条录上。并乞参商下语也。朱子答吴德夫书曰。静而此理已具。动而此用实行。则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则是易之有太极者也。昨来南轩尝谓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盖得之矣。
又答吴晦叔书曰。易变易也。兼指一动一静已发未发而言之也。太极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极。言即夫动静阖辟而皆有是理也。
又答程可久书曰。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后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极。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而非在阴阳之外也。
又答杨子直书曰。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馀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也。又曰谓太极含动静则可。(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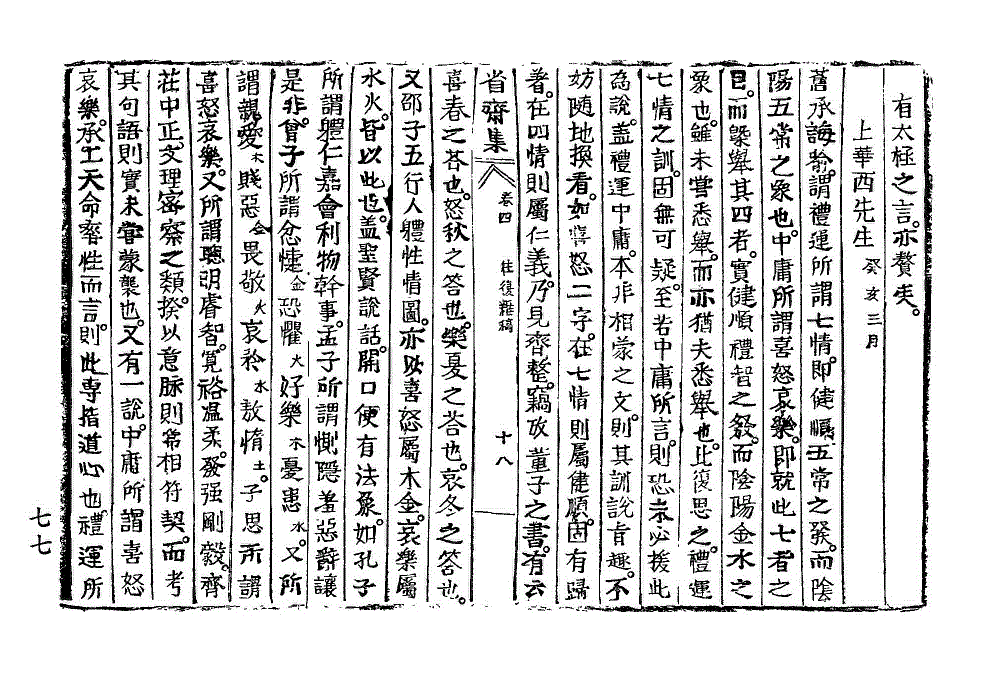 有太极之言。亦赘矣。
有太极之言。亦赘矣。上华西先生(癸亥三月)
旧承诲喻。谓礼运所谓七情。即健顺五常之发。而阴阳五常之象也。中庸所谓喜怒哀乐。即就此七者之目。而槩举其四者。实健顺礼智之发。而阴阳金水之象也。虽未尝悉举。而亦犹夫悉举也。比复思之。礼运七情之训。固无可疑。至若中庸所言。则恐未必援此为说。盖礼运中庸。本非相蒙之文。则其训说旨趣。不妨随地换看。如喜怒二字。在七情则属健顺。固有归着。在四情则属仁义。乃见齐整。窃考董子之书。有云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又邵子五行人体性情图。亦以喜怒属木金。哀乐属水火。皆以此也。盖圣贤说话。开口便有法象。如孔子所谓体仁嘉会利物干事。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曾子所谓忿懥(金)恐惧(火)好乐(木)忧患(水)。又所谓亲爱(木)贱恶(金)畏敬(火)哀矜(水)敖惰(土)。子思所谓喜怒哀乐。又所谓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之类。揆以意脉则常相符契。而考其句语则实未尝蒙袭也。又有一说。中庸所谓喜怒哀乐。承上天命率性而言。则此专指道心也。礼运所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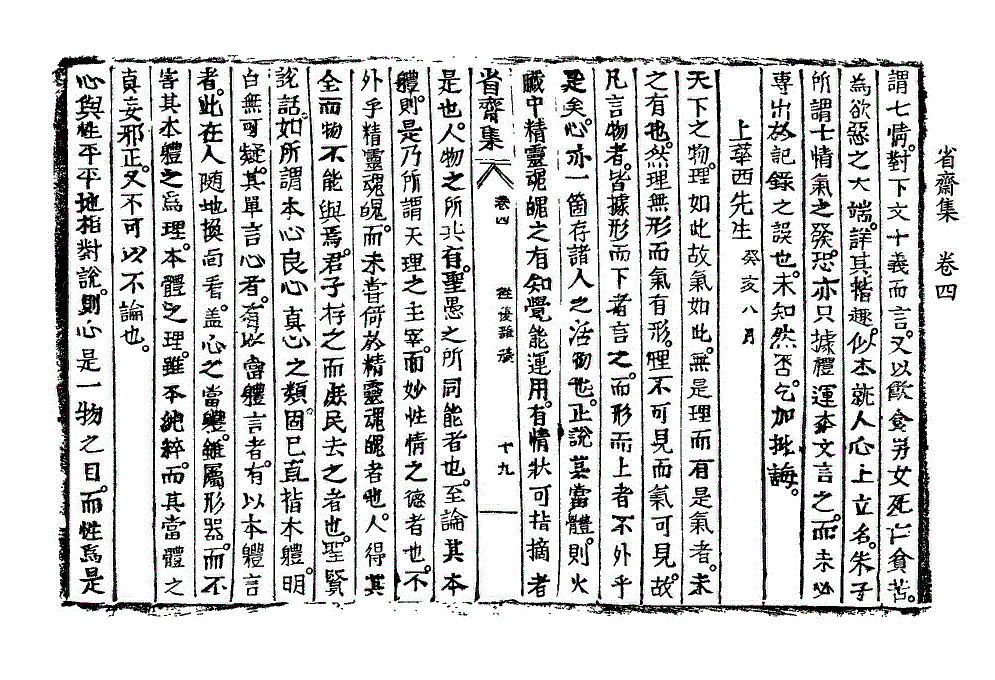 谓七情。对下文十义而言。又以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为欲恶之大端。详其指趣。似本就人心上立名。朱子所谓七情气之发。恐亦只据礼运本文言之。而未必专出于记录之误也。未知然否。乞加批诲。
谓七情。对下文十义而言。又以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为欲恶之大端。详其指趣。似本就人心上立名。朱子所谓七情气之发。恐亦只据礼运本文言之。而未必专出于记录之误也。未知然否。乞加批诲。上华西先生(癸亥八月)
天下之物。理如此故气如此。无是理而有是气者。未之有也。然理无形而气有形。理不可见而气可见。故凡言物者。皆据形而下者言之。而形而上者不外乎是矣。心亦一个存诸人之活物也。正说其当体。则火脏中精灵魂魄之有知觉能运用。有情状可指摘者是也。人物之所共有。圣愚之所同能者也。至论其本体。则是乃所谓天理之主宰。而妙性情之德者也。不外乎精灵魂魄。而未尝倚于精灵魂魄者也。人得其全而物不能与焉。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者也。圣贤说话。如所谓本心良心真心之类。固已直指本体。明白无可疑。其单言心者。有以当体言者。有以本体言者。此在人随地换面看。盖心之当体。虽属形器。而不害其本体之为理。本体之理。虽本纯粹。而其当体之真妄邪正。又不可以不论也。
心与性平平地相对说。则心是一物之目。而性为是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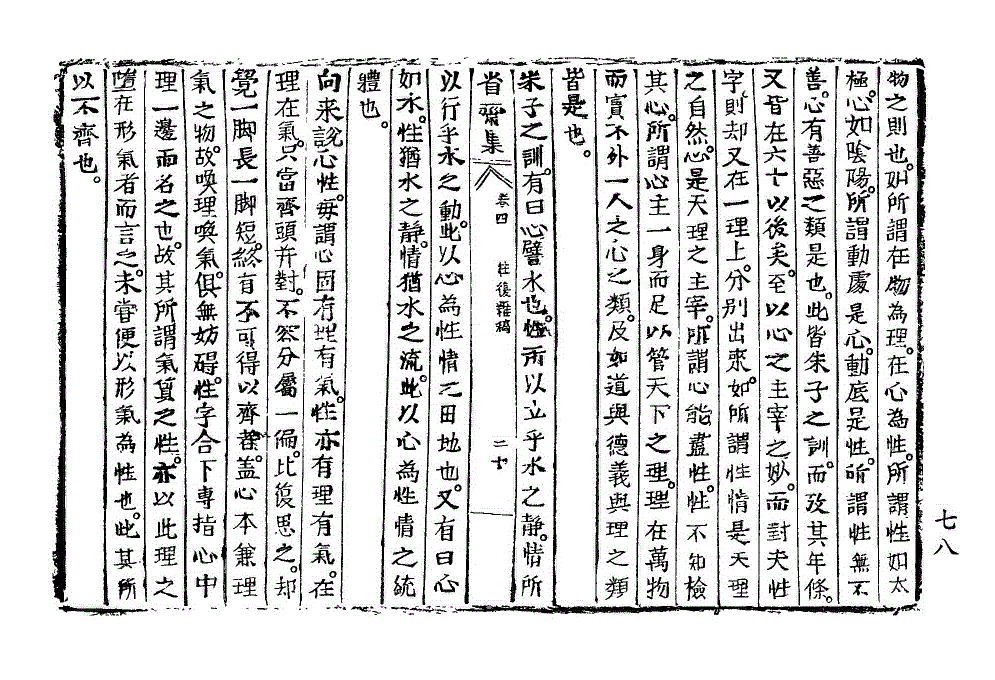 物之则也。如所谓在物为理。在心为性。所谓性如太极。心如阴阳。所谓动处是心。动底是性。所谓性无不善。心有善恶之类是也。此皆朱子之训。而考其年条。又皆在六十以后矣。至以心之主宰之妙。而对夫性字。则却又在一理上。分别出来。如所谓性情是天理之自然。心是天理之主宰。所谓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所谓心主一身而足以管天下之理。理在万物而实不外一人之心之类。及如道与德义与理之类皆是也。
物之则也。如所谓在物为理。在心为性。所谓性如太极。心如阴阳。所谓动处是心。动底是性。所谓性无不善。心有善恶之类是也。此皆朱子之训。而考其年条。又皆在六十以后矣。至以心之主宰之妙。而对夫性字。则却又在一理上。分别出来。如所谓性情是天理之自然。心是天理之主宰。所谓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所谓心主一身而足以管天下之理。理在万物而实不外一人之心之类。及如道与德义与理之类皆是也。朱子之训。有曰心譬水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此以心为性情之田地也。又有曰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犹水之流。此以心为性情之统体也。
向来说心性。每谓心固有理有气。性亦有理有气。在理在气。只当齐头并对。不容分属一偏。比复思之。却觉一脚长一脚短。终有不可得以齐者。盖心本兼理气之物。故唤理唤气。俱无妨碍。性字合下专指心中理一边而名之也。故其所谓气质之性。亦以此理之堕在形气者而言之。未尝便以形气为性也。此其所以不齐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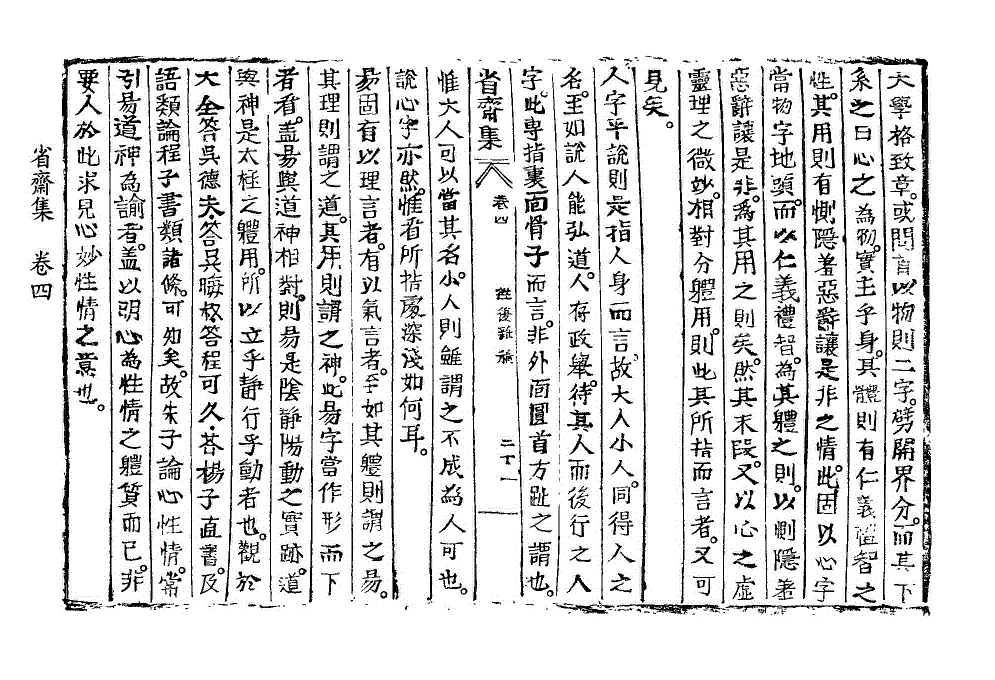 大学格致章。或问首以物则二字。劈开界分。而其下系之曰心之为物。实主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此固以心字当物字地头。而以仁义礼智。为其体之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其用之则矣。然其末段。又以心之虚灵理之微妙。相对分体用。则此其所指而言者。又可见矣。
大学格致章。或问首以物则二字。劈开界分。而其下系之曰心之为物。实主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此固以心字当物字地头。而以仁义礼智。为其体之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其用之则矣。然其末段。又以心之虚灵理之微妙。相对分体用。则此其所指而言者。又可见矣。人字平说则是指人身而言。故大人小人。同得人之名。至如说人能弘道。人存政举。待其人而后行之人字。此专指里面骨子而言。非外面圆首方趾之谓也。惟大人可以当其名。小人则虽谓之不成为人可也。说心字亦然。惟看所指处深浅如何耳。
易固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至如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易字当作形而下者看。盖易与道神相对。则易是阴静阳动之实迹。道与神是太极之体用。所以立乎静行乎动者也。观于大全答吴德夫,答吴晦叔,答程可久,答杨子直书。及语类论程子书类诸条。可知矣。故朱子论心性情。常引易道神为谕者。盖以明心为性情之体质而已。非要人于此求见心妙性情之意也。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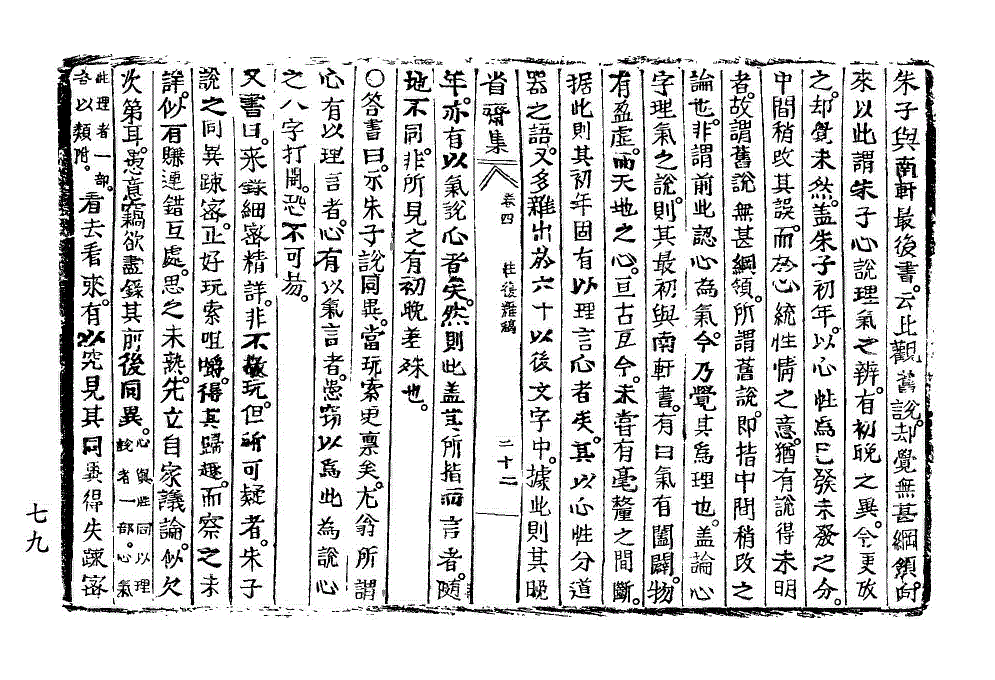 朱子与南轩最后书。云比观旧说。却觉无甚纲领。向来以此谓朱子心说理气之辨。有初晚之异。今更考之。却觉未然。盖朱子初年。以心性为已发未发之分。中间稍改其误。而于心统性情之意。犹有说得未明者。故谓旧说无甚纲领。所谓旧说。即指中间稍改之论也。非谓前此认心为气。今乃觉其为理也。盖论心字理气之说。则其最初与南轩书。有曰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亘古亘今。未尝有毫釐之间断。据此则其初年固有以理言心者矣。其以心性分道器之语。又多杂出于六十以后文字中。据此则其晚年。亦有以气说心者矣。然则此盖其所指而言者。随地不同。非所见之有初晚差殊也。
朱子与南轩最后书。云比观旧说。却觉无甚纲领。向来以此谓朱子心说理气之辨。有初晚之异。今更考之。却觉未然。盖朱子初年。以心性为已发未发之分。中间稍改其误。而于心统性情之意。犹有说得未明者。故谓旧说无甚纲领。所谓旧说。即指中间稍改之论也。非谓前此认心为气。今乃觉其为理也。盖论心字理气之说。则其最初与南轩书。有曰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亘古亘今。未尝有毫釐之间断。据此则其初年固有以理言心者矣。其以心性分道器之语。又多杂出于六十以后文字中。据此则其晚年。亦有以气说心者矣。然则此盖其所指而言者。随地不同。非所见之有初晚差殊也。○答书曰。示朱子说同异。当玩索更禀矣。尤翁所谓心有以理言者。心有以气言者。愚窃以为此为说心之八字打开。恐不可易。
又书曰。来录细密精详。非不敬玩。但所可疑者。朱子说之同异疏密。正好玩索咀嚼。得其归趣。而察之未详。似有赚连错互处。思之未熟。先立自家议论。似欠次第耳。愚意窃欲尽录其前后同异。(心与性同以理说者一部。心气性理者一部。各以类附。)看去看来。有以究见其同异得失疏密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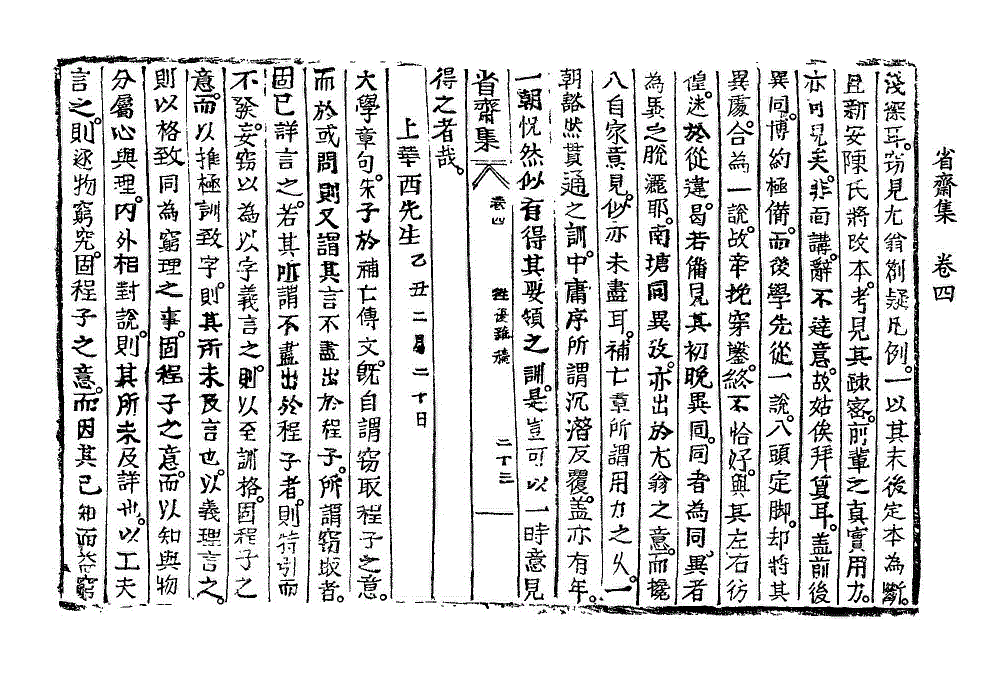 浅深耳。窃见尤翁劄疑凡例。一以其末后定本为断。且新安陈氏将改本。考见其疏密。前辈之真实用力。亦可见矣。非面讲。辞不达意。故姑俟拜质耳。盖前后异同。博约极备。而后学先从一说。入头定脚。却将其异处。合为一说。故牵挽穿凿。终不恰好。与其左右彷徨。迷于从违。曷若备见其初晚异同。同者为同。异者为异之脱洒耶。南塘同异考。亦出于尤翁之意。而搀入自家意见。似亦未尽耳。补亡章所谓用力之久。一朝豁然贯通之训。中庸序所谓沉潜反覆。盖亦有年。一朝恍然似有得其要领之训。是岂可以一时意见得之者哉。
浅深耳。窃见尤翁劄疑凡例。一以其末后定本为断。且新安陈氏将改本。考见其疏密。前辈之真实用力。亦可见矣。非面讲。辞不达意。故姑俟拜质耳。盖前后异同。博约极备。而后学先从一说。入头定脚。却将其异处。合为一说。故牵挽穿凿。终不恰好。与其左右彷徨。迷于从违。曷若备见其初晚异同。同者为同。异者为异之脱洒耶。南塘同异考。亦出于尤翁之意。而搀入自家意见。似亦未尽耳。补亡章所谓用力之久。一朝豁然贯通之训。中庸序所谓沉潜反覆。盖亦有年。一朝恍然似有得其要领之训。是岂可以一时意见得之者哉。上华西先生(乙丑二月二十日)
大学章句。朱子于补亡传文。既自谓窃取程子之意。而于或问则又谓其言不尽出于程子。所谓窃取者。固已详言之。若其所谓不尽出于程子者。则特引而不发。妄窃以为以字义言之。则以至训格。固程子之意。而以推极训致字。则其所未及言也。以义理言之。则以格致同为穷理之事。固程子之意。而以知与物分属心与理。内外相对说。则其所未及详也。以工夫言之。则逐物穷究。固程子之意。而因其已知而益穷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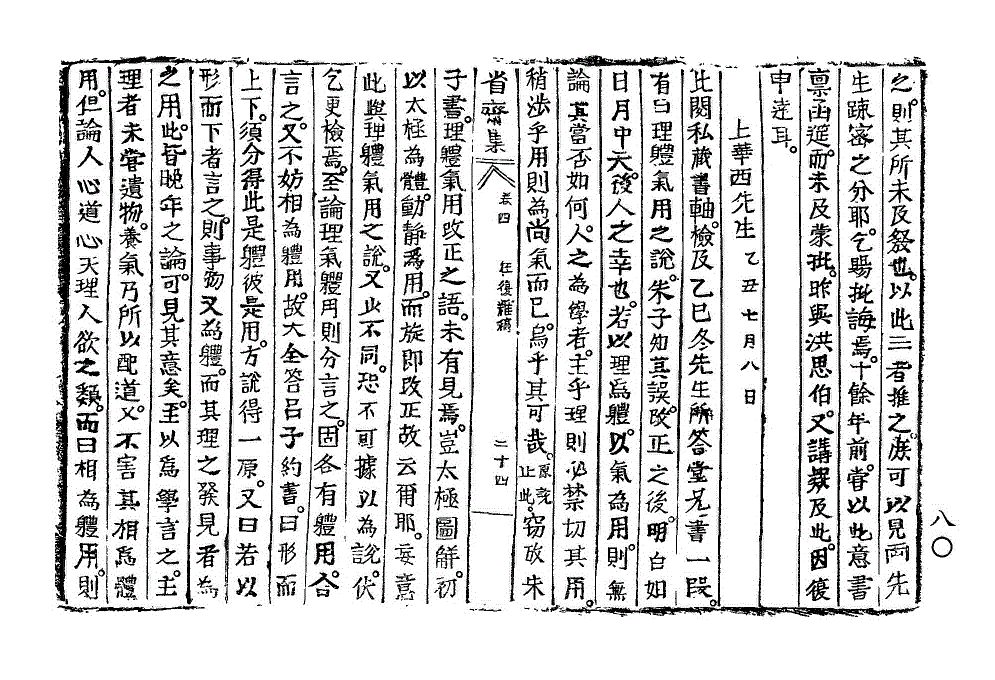 之。则其所未及发也。以此三者推之。庶可以见两先生疏密之分耶。乞赐批诲焉。十馀年前。尝以此意书禀函筵。而未及蒙批。昨与洪思伯。又讲疑及此。因复申达耳。
之。则其所未及发也。以此三者推之。庶可以见两先生疏密之分耶。乞赐批诲焉。十馀年前。尝以此意书禀函筵。而未及蒙批。昨与洪思伯。又讲疑及此。因复申达耳。上华西先生(乙丑七月八日)
比阅私藏书轴。检及乙巳冬先生所答堂兄书一段。有曰理体气用之说。朱子知其误。改正之后。明白如日月中天。后人之幸也。若以理为体。以气为用。则无论其当否如何。人之为学者。主乎理则必禁切其用。稍涉乎用则为尚气而已。乌乎其可哉。(原说止此。)窃考朱子书。理体气用改正之语。未有见焉。岂太极图解。初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而旋即改正故云尔耶。妄意此与理体气用之说。又少不同。恐不可据以为说。伏乞更检焉。至论理气体用则分言之。固各有体用。合言之。又不妨相为体用。故大全答吕子约书。曰形而上下。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方说得一原。又曰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此皆晚年之论。可见其意矣。至以为学言之。主理者未尝遗物。养气乃所以配道。又不害其相为体用。但论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之类。而曰相为体用。则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不成伦理。诚如下教之意矣。未知如何。伏乞赐教焉。(形而上下。固即是理气。然其所主而名则亦自有分。若以论形而上下者。一例移施于理气。则有说不去处矣。此书所论。当更商之。)
不成伦理。诚如下教之意矣。未知如何。伏乞赐教焉。(形而上下。固即是理气。然其所主而名则亦自有分。若以论形而上下者。一例移施于理气。则有说不去处矣。此书所论。当更商之。)上华西先生(乙丑七月十八日)
昨夕拜下覆。谨领诸诲。但家僮口传泄患比添。伏用闷虑。夜来气候更何如。不至大损耶。今得京报。城东诸寝所。雨后崩损处甚多。至有大臣率诸僚奉审之举。普切震懔耳。下示所辨困知记象已成无可免之说。谨闻命矣。盖如其言。则大易所谓迁善改过。财成辅相之类。皆将为无施之空言。岂可乎哉。但象已成一句。则活看似无病。如程子曰冲漠无眹。万象森然已具。此象字以理言。无未成已成之可言。朱子曰象数未判。而其理已具。此象字以气言。有未成已成之时分矣。今若以气言则岂有所碍耶。粗说则如人生堕地。始有修短定命之类是也。未知如何。伏乞再教焉。疾雷破柱。如何动得他云云。重教虽驽弱。敢不增气服膺乎。因便付候。伏惟下察。
上华西先生(丁卯夏)
比将静庵先生遗集。温习数过。其进讲论理气处。有曰理为气之主而气为理之所使一段。极明白无可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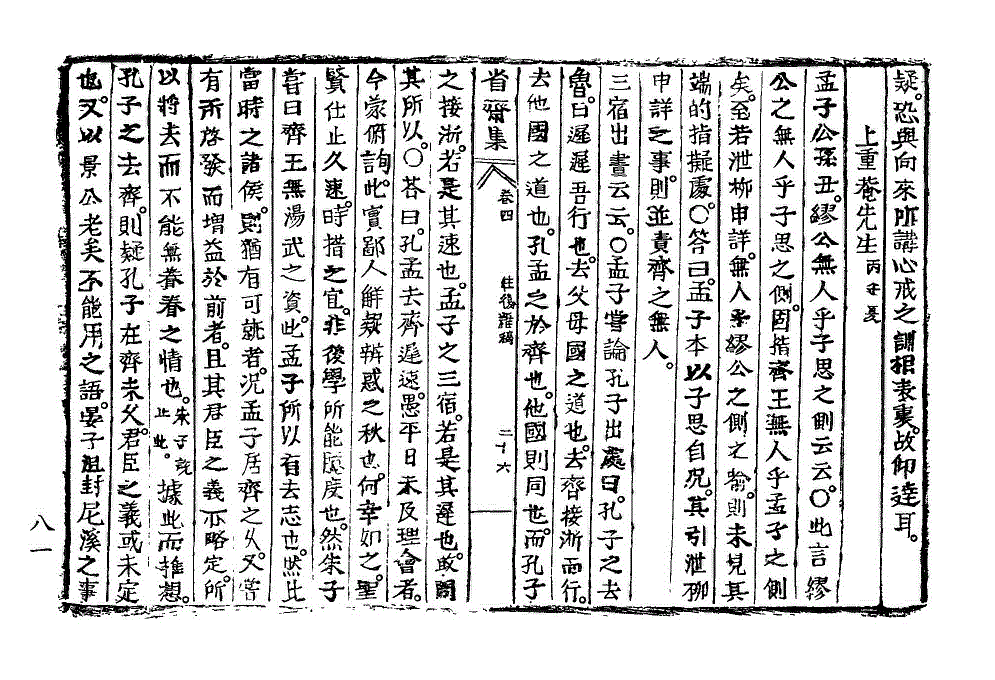 疑。恐与向来所讲心戒之训相表里。故仰达耳。
疑。恐与向来所讲心戒之训相表里。故仰达耳。上重庵先生(丙午夏)
孟子公孙丑。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云云。○此言缪公之无人乎子思之侧。固指齐王无人乎孟子之侧矣。至若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之喻。则未见其端的指拟处。○答曰。孟子本以子思自况。其引泄柳申详之事。则并责齐之无人。
三宿出昼云云。○孟子尝论孔子出处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孔孟之于齐也。他国则同也。而孔子之接淅。若是其速也。孟子之三宿。若是其迟也。敢问其所以。○答曰。孔孟去齐迟速。愚平日未及理会者。今蒙俯询。此实鄙人解疑辨惑之秋也。何幸如之。圣贤仕止久速。时措之宜。非后学所能臆度也。然朱子尝曰齐王无汤武之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当时之诸侯。则犹有可就者。况孟子居齐之久。又尝有所启发而增益于前者。且其君臣之义亦略定。所以将去而不能无眷眷之情也。(朱子说止此。)据此而推想。孔子之去齐。则疑孔子在齐未久。君臣之义或未定也。又以景公老矣不能用之语。晏子沮封尼溪之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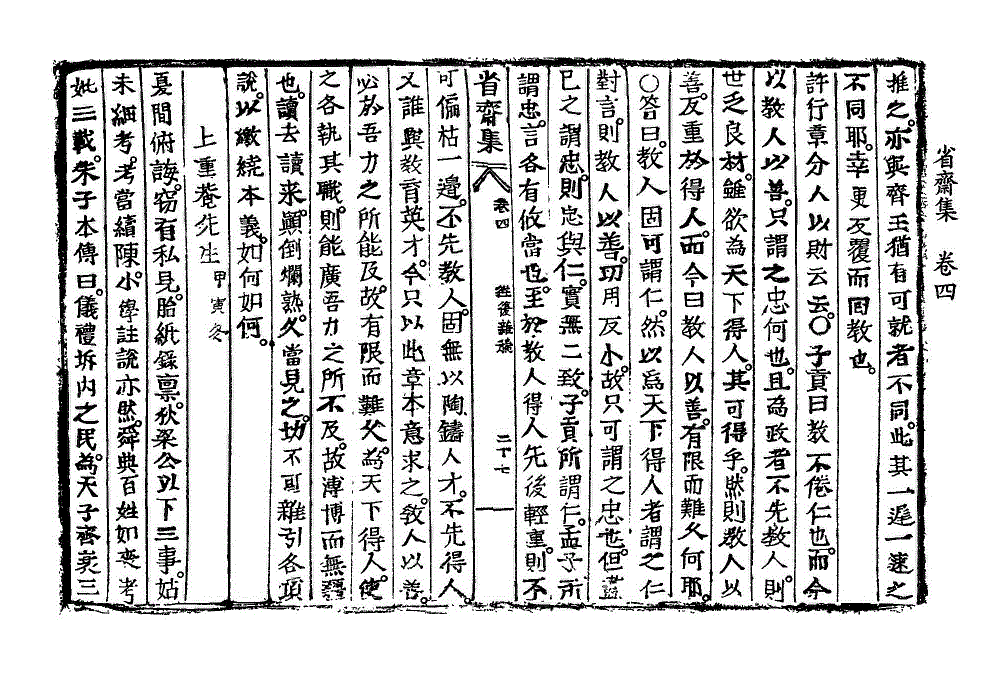 推之。亦与齐王犹有可就者不同。此其一迟一速之不同耶。幸更反覆而回教也。
推之。亦与齐王犹有可就者不同。此其一迟一速之不同耶。幸更反覆而回教也。许行章分人以财云云。○子贡曰教不倦仁也。而今以教人以善。只谓之忠何也。且为政者不先教人。则世乏良材。虽欲为天下得人。其可得乎。然则教人以善。反重于得人。而今曰教人以善。有限而难久何耶。○答曰。教人固可谓仁。然以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对言。则教人以善。功用反小。故只可谓之忠也。但尽己之谓忠。则忠与仁。实无二致。子贡所谓仁。孟子所谓忠。言各有攸当也。至于教人得人先后轻重。则不可偏枯一边。不先教人。固无以陶铸人才。不先得人。又谁与教育英才。今只以此章本意求之。教人以善。必于吾力之所能及。故有限而难久。为天下得人。使之各执其职。则能广吾力之所不及。故溥博而无疆也。读去读来。颠倒烂熟。久当见之。切不可杂引各项说。以缴绕本义。如何如何。
上重庵先生(甲寅冬)
夏间俯诲。窃有私见。胎纸录禀。狄梁公以下三事。姑未细考。考当续陈。小学注说亦然。舜典百姓如丧考妣三载。朱子本传曰。仪礼圻内之民。为天子齐衰三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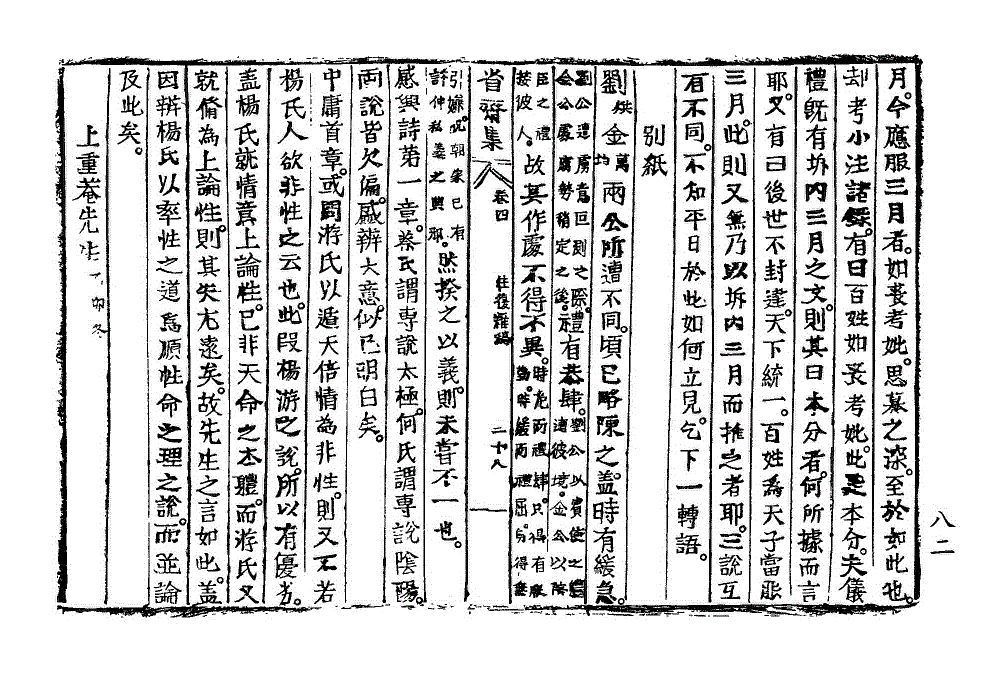 月。今应服三月者。如丧考妣。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却考小注诸录。有曰百姓如丧考妣。此是本分。夫仪礼既有圻内三月之文。则其曰本分者。何所据而言耶。又有曰后世不封建。天下统一。百姓为天子当服三月。此则又无乃以圻内三月而推之者耶。三说互有不同。不知平日于此如何立见。乞下一转语。
月。今应服三月者。如丧考妣。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却考小注诸录。有曰百姓如丧考妣。此是本分。夫仪礼既有圻内三月之文。则其曰本分者。何所据而言耶。又有曰后世不封建。天下统一。百姓为天子当服三月。此则又无乃以圻内三月而推之者耶。三说互有不同。不知平日于此如何立见。乞下一转语。别纸
刘(烘)金(万均)两公所遭不同。顷已略陈之。盖时有缓急。(刘公遭虏意叵测之际。金公处虏势稍定之后。)礼有恭肆。(刘公以宾使之体适彼境。金公以陪臣之礼接彼人。)故其作处不得不异。(时危而礼肆。只得有殷勤。时缓而礼屈。乌得无引嫌。况朝家已有许伸私义之典邪。)然揆之以义。则未尝不一也。
感兴诗第一章。蔡氏谓专说太极。何氏谓专说阴阳。两说皆欠偏。盛辨大意。似已明白矣。
中庸首章。或问游氏以遁天倍情为非性。则又不若杨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此段杨游之说。所以有优劣。盖杨氏就情意上论性。已非天命之本体。而游氏又就脩为上论性。则其失尤远矣。故先生之言如此。盖因辨杨氏以率性之道为顺性命之理之说。而并论及此矣。
上重庵先生(乙卯冬)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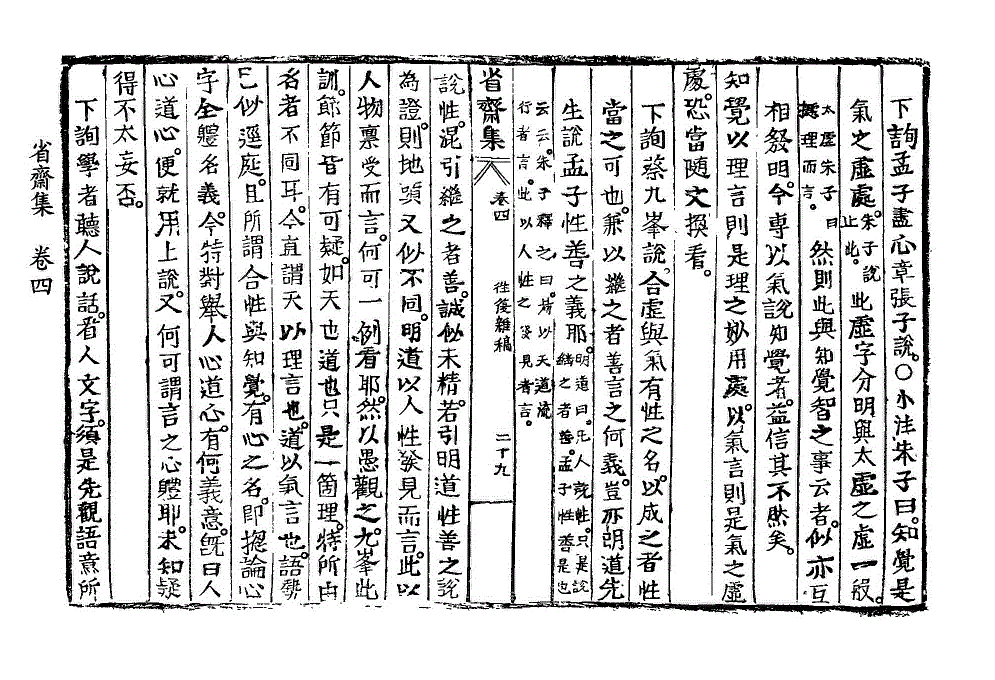 下询孟子尽心章张子说。○小注朱子曰。知觉是气之虚处。(朱子说止此。)此虚字分明与太虚之虚一般。(太虚朱子曰据理而言。)然则此与知觉智之事云者。似亦互相发明。今专以气说知觉者。益信其不然矣。
下询孟子尽心章张子说。○小注朱子曰。知觉是气之虚处。(朱子说止此。)此虚字分明与太虚之虚一般。(太虚朱子曰据理而言。)然则此与知觉智之事云者。似亦互相发明。今专以气说知觉者。益信其不然矣。知觉以理言则是理之妙用处。以气言则是气之虚处。恐当随文换看。
下询蔡九峰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以成之者性当之可也。兼以继之者善言之何义。岂亦明道先生说孟子性善之义耶。(明道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性善是也云云。朱子释之曰。易以天道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发见者言。)
说性。混引继之者善。诚似未精。若引明道性善之说为證。则地头又似不同。明道以人性发见而言。此以人物禀受而言。何可一例看耶。然以愚观之。九峰此训。节节皆有可疑。如天也道也只是一个理。特所由名者不同耳。今直谓天以理言也。道以气言也。语势已似径庭。且所谓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即揔论心字全体名义。今特对举人心道心。有何义意。既曰人心道心。便就用上说。又何可谓言之心体耶。未知疑得不太妄否。
下询学者听人说话。看人文字。须是先观语意所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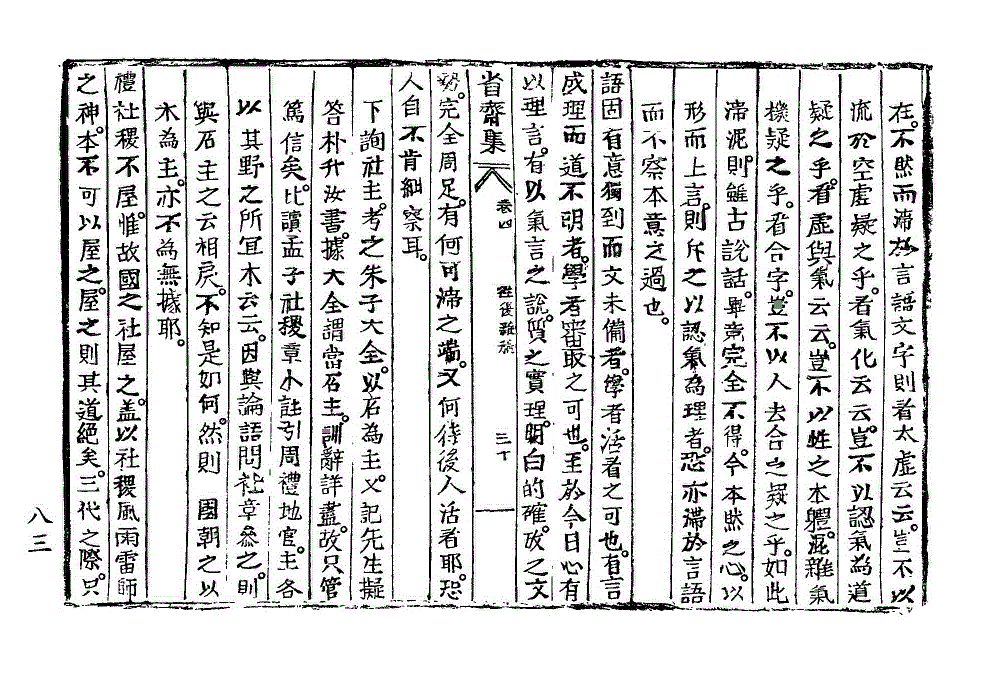 在。不然而滞于言语文字则看太虚云云。岂不以流于空虚疑之乎。看气化云云。岂不以认气为道疑之乎。看虚与气云云。岂不以性之本体。混杂气机疑之乎。看合字。岂不以人去合之疑之乎。如此滞泥。则虽古说话。毕竟完全不得。今本然之心。以形而上言。则斥之以认气为理者。恐亦滞于言语而不察本意之过也。
在。不然而滞于言语文字则看太虚云云。岂不以流于空虚疑之乎。看气化云云。岂不以认气为道疑之乎。看虚与气云云。岂不以性之本体。混杂气机疑之乎。看合字。岂不以人去合之疑之乎。如此滞泥。则虽古说话。毕竟完全不得。今本然之心。以形而上言。则斥之以认气为理者。恐亦滞于言语而不察本意之过也。语固有意独到而文未备者。学者活看之可也。有言成理而道不明者。学者审取之可也。至于今日心有以理言。有以气言之说。质之实理。明白的确。考之文势。完全周足。有何可滞之端。又何待后人活看耶。恐人自不肯细察耳。
下询社主。考之朱子大全。以石为主。又记先生拟答朴升汝书。据大全谓当石主。训辞详尽。故只管笃信矣。比读孟子社稷章小注引周礼地官。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云云。因与论语问社章参之。则与石主之云相戾。不知是如何。然则 国朝之以木为主。亦不为无据耶。
礼社稷不屋。惟故国之社屋之。盖以社稷风雨雷师之神。本不可以屋之。屋之则其道绝矣。三代之际。只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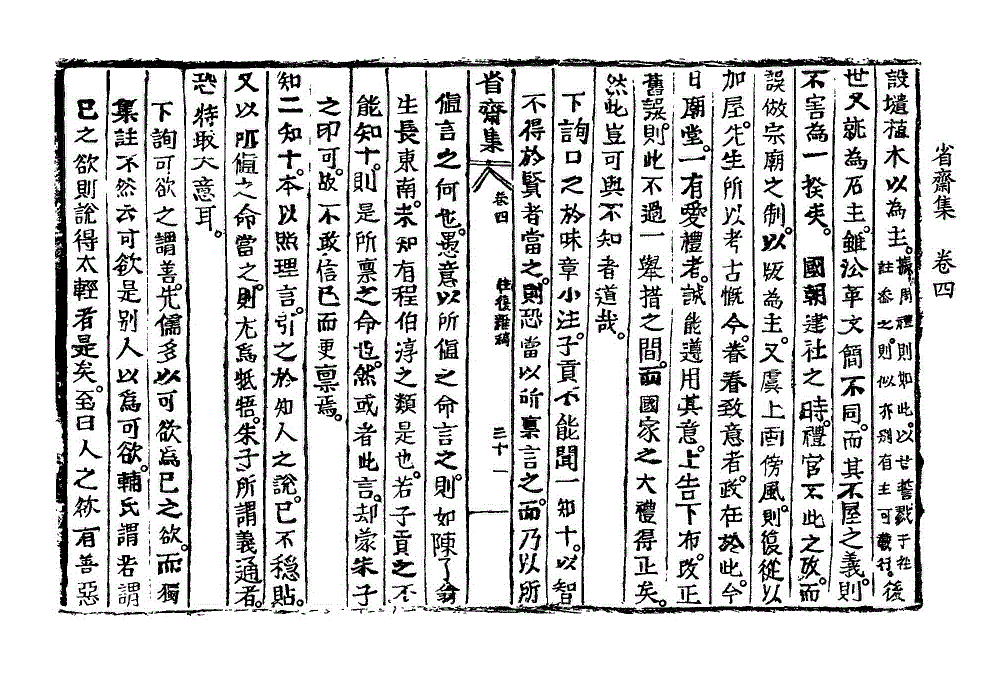 设壝植木以为主。(据周礼则如此。以甘誓戮于社注参之。则似亦别有主可载行。)后世又就为石主。虽沿革文简不同。而其不屋之义。则不害为一揆矣。 国朝建社之时。礼官不此之考。而误仿宗庙之制。以版为主。又虞上两傍风。则复从以加屋。先生所以考古慨今。眷眷致意者。政在于此。今日庙堂。一有爱礼者。诚能遵用其意。上告下布。改正旧误。则此不过一举措之间。而国家之大礼得正矣。然此岂可与不知者道哉。
设壝植木以为主。(据周礼则如此。以甘誓戮于社注参之。则似亦别有主可载行。)后世又就为石主。虽沿革文简不同。而其不屋之义。则不害为一揆矣。 国朝建社之时。礼官不此之考。而误仿宗庙之制。以版为主。又虞上两傍风。则复从以加屋。先生所以考古慨今。眷眷致意者。政在于此。今日庙堂。一有爱礼者。诚能遵用其意。上告下布。改正旧误。则此不过一举措之间。而国家之大礼得正矣。然此岂可与不知者道哉。下询口之于味章小注。子贡不能闻一知十。以智不得于贤者当之。则恐当以所禀言之。而乃以所值言之何也。愚意以所值之命言之。则如陈了翁生长东南。未知有程伯淳之类是也。若子贡之不能知十。则是所禀之命也。然或者此言。却蒙朱子之印可。故不敢信己而更禀焉。
知二知十。本以照理言。引之于知人之说。已不稳贴。又以所值之命当之。则尤为牴牾。朱子所谓义通者。恐特取大意耳。
下询可欲之谓善。先儒多以可欲为己之欲。而独集注不然云可欲是别人以为可欲。辅氏谓若谓己之欲则说得太轻者是矣。至曰人之欲有善恶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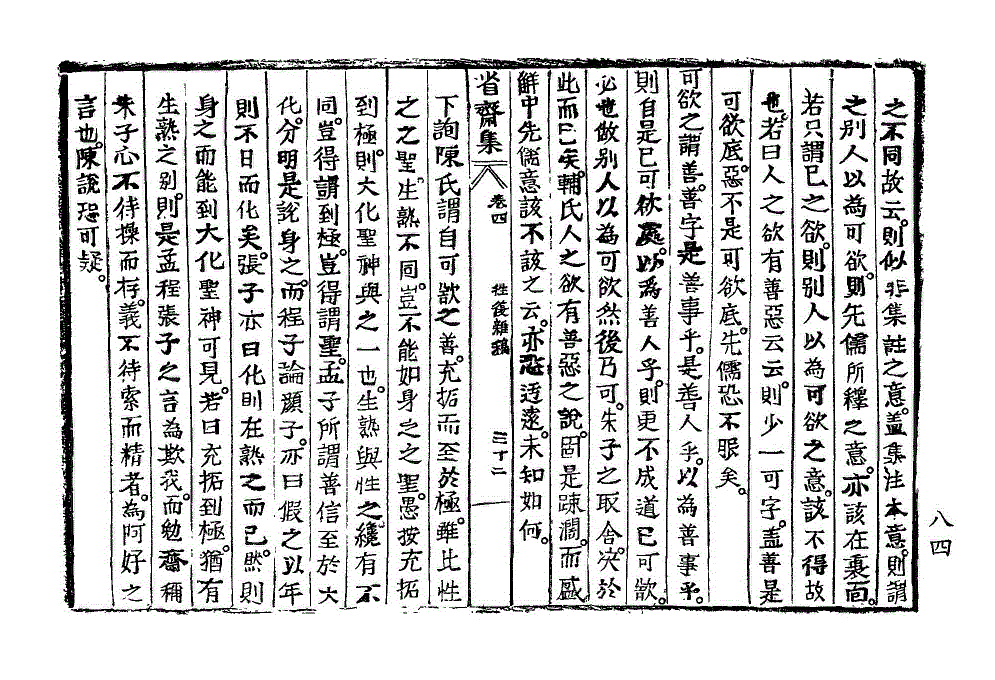 之不同故云。则似非集注之意。盖集注本意。则谓之别人以为可欲。则先儒所释之意。亦该在里面。若只谓己之欲。则别人以为可欲之意。该不得故也。若曰人之欲有善恶云云。则少一可字。盖善是可欲底。恶不是可欲底。先儒恐不服矣。
之不同故云。则似非集注之意。盖集注本意。则谓之别人以为可欲。则先儒所释之意。亦该在里面。若只谓己之欲。则别人以为可欲之意。该不得故也。若曰人之欲有善恶云云。则少一可字。盖善是可欲底。恶不是可欲底。先儒恐不服矣。可欲之谓善。善字是善事乎。是善人乎。以为善事乎。则自是己可欲处。以为善人乎。则更不成道己可欲。必也做别人以为可欲然后乃可。朱子之取舍。决于此而已矣。辅氏人之欲有善恶之说。固是疏阔。而盛解中先儒意该不该之云。亦恐迂远。未知如何。
下询陈氏谓自可欲之善。充拓而至于极。虽比性之之圣。生熟不同。岂不能如身之之圣。愚按充拓到极。则大化圣神与之一也。生熟与性之。才有不同。岂得谓到极。岂得谓圣。孟子所谓善信至于大化。分明是说身之。而程子论颜子。亦曰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张子亦曰化则在熟之而已。然则身之而能到大化圣神可见。若曰充拓到极。犹有生熟之别。则是孟程张子之言为欺我。而勉斋称朱子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者。为阿好之言也。陈说恐可疑。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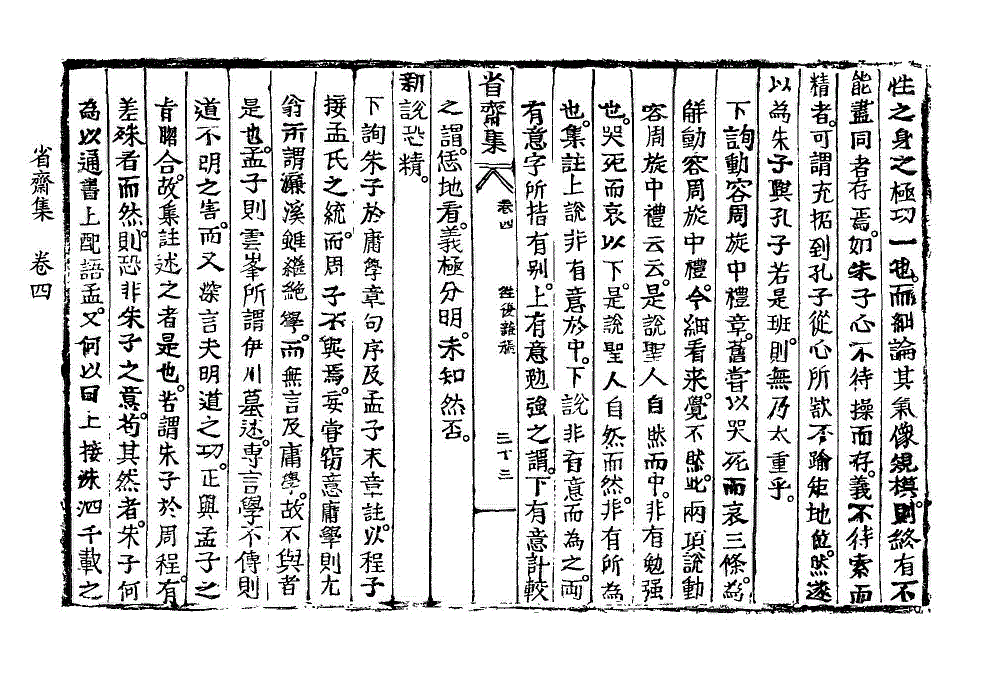 性之身之极功一也。而细论其气像规模。则终有不能尽同者存焉。如朱子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者。可谓充拓到孔子从心所欲不踰矩地位。然遂以为朱子与孔子若是班。则无乃太重乎。
性之身之极功一也。而细论其气像规模。则终有不能尽同者存焉。如朱子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者。可谓充拓到孔子从心所欲不踰矩地位。然遂以为朱子与孔子若是班。则无乃太重乎。下询动容周旋中礼章。旧尝以哭死而哀三条。为解动容周旋中礼。今细看来。觉不然。此两项说动容周旋中礼云云。是说圣人自然而中。非有勉强也。哭死而哀以下。是说圣人自然而然。非有所为也。集注上说非有意于中。下说非有意而为之。两有意字所指有别。上有意勉强之谓。下有意计较之谓。恁地看。义极分明。未知然否。
新说恐精。
下询朱子于庸学章句序及孟子末章注。以程子接孟氏之统。而周子不与焉。妄尝窃意庸学则尤翁所谓濂溪虽继绝学。而无言及庸学。故不与者是也。孟子则云峰所谓伊川墓述。专言学不传则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与孟子之旨吻合。故集注述之者是也。若谓朱子于周程。有差殊看而然。则恐非朱子之意。苟其然者。朱子何为以通书上配语孟。又何以曰上接洙泗千载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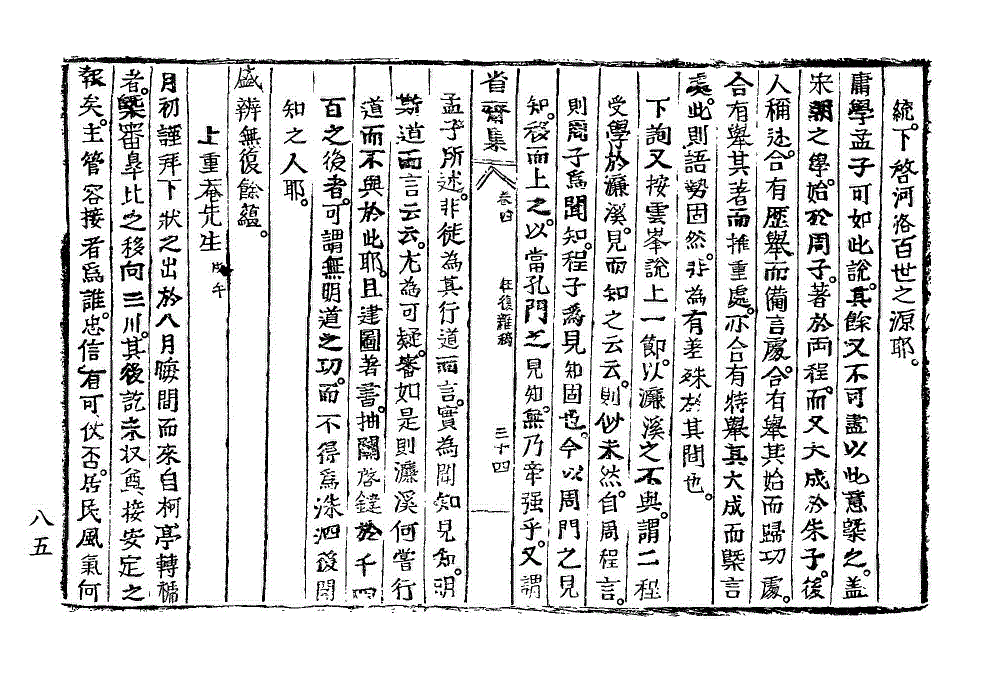 统。下启河洛百世之源耶。
统。下启河洛百世之源耶。庸学孟子可如此说。其馀又不可尽以此意槩之。盖宋朝之学。始于周子。著于两程。而又大成于朱子。后人称述。合有历举而备言处。合有举其始而归功处。合有举其著而推重处。亦合有特举其大成而槩言处。此则语势固然。非为有差殊于其间也。
下询又按云峰说上一节。以濂溪之不与。谓二程受学于濂溪。见而知之云云。则似未然。自周程言。则周子为闻知。程子为见知固也。今以周门之见知。移而上之。以当孔门之见知。无乃牵强乎。又谓孟子所述。非徒为其行道而言。实为闻知见知。明斯道而言云云。尤为可疑。审如是则濂溪何尝行道而不与于此耶。且建图著书。抽关启键于千四百之后者。可谓无明道之功。而不得为洙泗后闻知之人耶。
盛辨无复馀蕴。
上重庵先生(戊午)
月初谨拜下状之出于八月晦间而来自柯亭转褫者。槩审皋比之移向三川。其后讫未收奠接安定之报矣。主管容接者为谁。忠信有可仗否。居民风气何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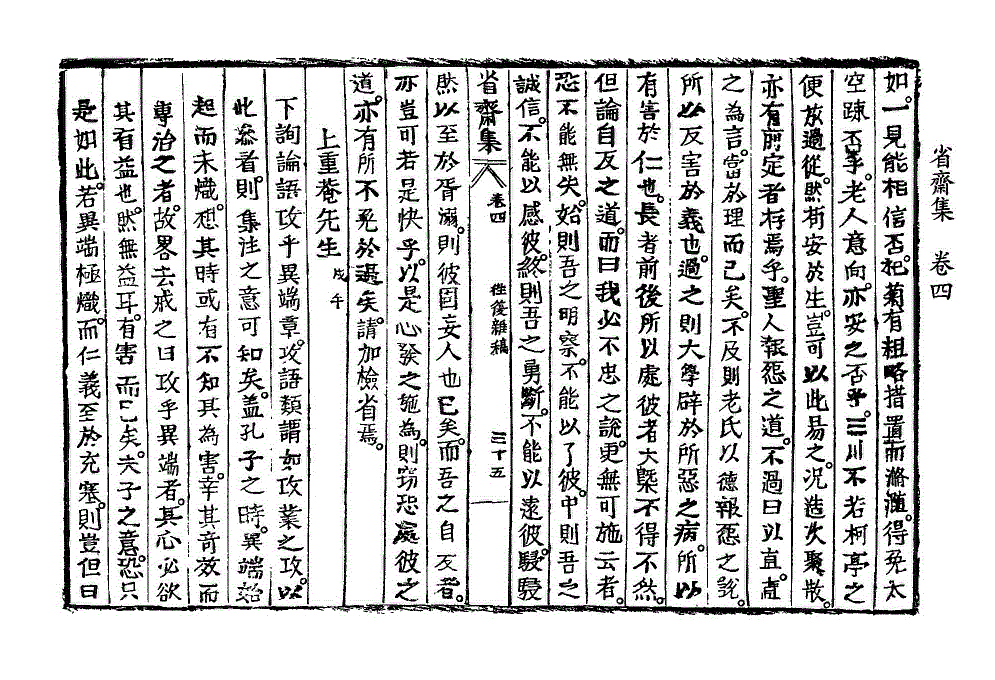 如。一见能相信否。杞菊有粗略措置而滫瀡。得免太空疏否乎。老人意向。亦安之否乎。三川不若柯亭之便于过从。然苟安于生。岂可以此易之。况造次聚散。亦有前定者存焉乎。圣人报怨之道。不过曰以直。直之为言。当于理而已矣。不及则老氏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反害于义也。过之则大学辟于所恶之病。所以有害于仁也。长者前后所以处彼者大槩不得不然。但论自反之道。而曰我必不忠之说。更无可施云者。恐不能无失。始则吾之明察。不能以了彼。中则吾之诚信。不能以感彼。终则吾之勇断。不能以远彼。骎骎然以至于胥溺。则彼固妄人也已矣。而吾之自反者。亦岂可若是快乎。以是心发之施为。则窃恐处彼之道。亦有所不免于过矣。请加检省焉。
如。一见能相信否。杞菊有粗略措置而滫瀡。得免太空疏否乎。老人意向。亦安之否乎。三川不若柯亭之便于过从。然苟安于生。岂可以此易之。况造次聚散。亦有前定者存焉乎。圣人报怨之道。不过曰以直。直之为言。当于理而已矣。不及则老氏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反害于义也。过之则大学辟于所恶之病。所以有害于仁也。长者前后所以处彼者大槩不得不然。但论自反之道。而曰我必不忠之说。更无可施云者。恐不能无失。始则吾之明察。不能以了彼。中则吾之诚信。不能以感彼。终则吾之勇断。不能以远彼。骎骎然以至于胥溺。则彼固妄人也已矣。而吾之自反者。亦岂可若是快乎。以是心发之施为。则窃恐处彼之道。亦有所不免于过矣。请加检省焉。上重庵先生(戊午)
下询论语攻乎异端章。攻语类谓如攻业之攻。以此参看。则集注之意可知矣。盖孔子之时。异端始起而未炽。想其时或有不知其为害。幸其奇效而专治之者。故略去戒之曰攻乎异端者。其心必欲其有益也。然无益耳。有害而已矣。夫子之意。恐只是如此。若异端极炽。而仁义至于充塞。则岂但曰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6L 页
 专治而后为害哉。故程子曰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朱子曰不惟说不可专治。便略去理会他也不得。又程子一生。不看庄列书。宋公基隆案上。置尹鑴中庸注。尤翁掷地骂之。使不得经眼。学者若以夫子之言。为攻之然后方有害。有略去理会之心。则大有所害。此不可不知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愚当初误看。以为如子夏小道致远恐泥。程子书札一向好着。亦自丧志之类。以此答洪斯文问藁矣。追思大不然。若然则是攻之然后为异端。非本文之义也。今改旧见如右所云。行当以示洪友。而第未知又无差缪否耳。
专治而后为害哉。故程子曰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朱子曰不惟说不可专治。便略去理会他也不得。又程子一生。不看庄列书。宋公基隆案上。置尹鑴中庸注。尤翁掷地骂之。使不得经眼。学者若以夫子之言。为攻之然后方有害。有略去理会之心。则大有所害。此不可不知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愚当初误看。以为如子夏小道致远恐泥。程子书札一向好着。亦自丧志之类。以此答洪斯文问藁矣。追思大不然。若然则是攻之然后为异端。非本文之义也。今改旧见如右所云。行当以示洪友。而第未知又无差缪否耳。旧解甚差。改之固当。但其改说。又有未尽。盖此章之旨。深味斯害也已四字。当作专治愈有害看。今作专治始有害看。此所谓未尽也。盖专治愈有害。则略治己有害可知。而语意浑全。该得终始。专治始有害。则略治也无害。而语意疏略。带得罅漏。所以必就异端未炽时言之。而及到极炽时节。却将后贤说添补然后意乃备。孔门说话。何尝见有此等处耶。至若朱子不惟说不可专治之训。特救或人问说之偏。非欲有补于本文言外之意也。未知何如。细考更教焉。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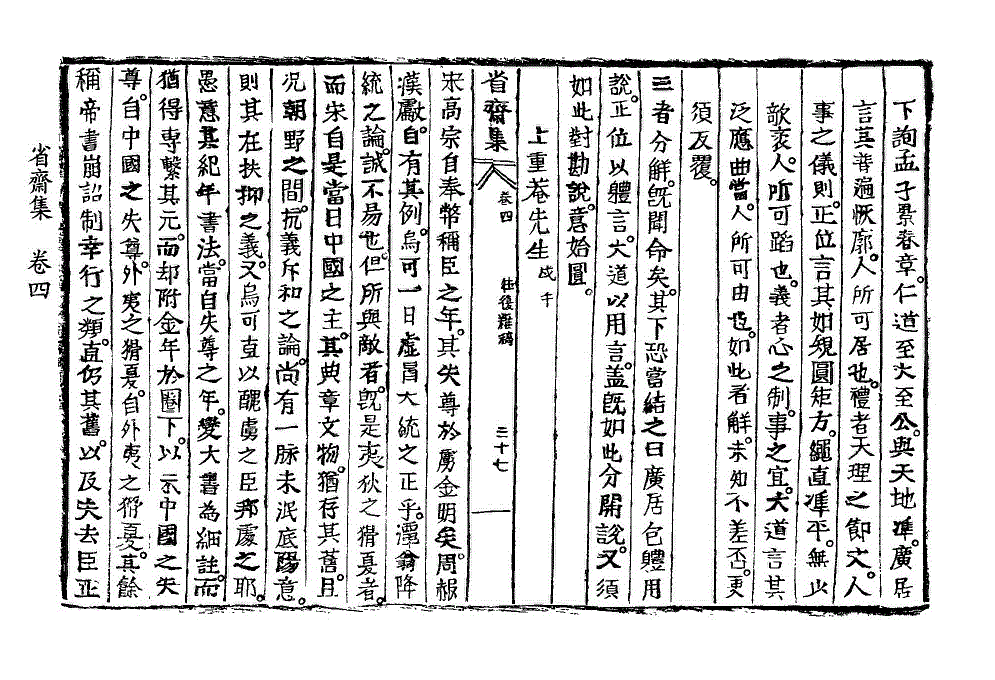 下询孟子景春章。仁道至大至公。与天地准。广居言其普遍恢廓。人所可居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正位言其如规圆矩方。绳直准平。无少欹袤。人所可蹈也。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大道言其泛应曲当。人所可由也。如此看解。未知不差否。更须反覆。
下询孟子景春章。仁道至大至公。与天地准。广居言其普遍恢廓。人所可居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正位言其如规圆矩方。绳直准平。无少欹袤。人所可蹈也。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大道言其泛应曲当。人所可由也。如此看解。未知不差否。更须反覆。三者分解。既闻命矣。其下恐当结之曰广居包体用说。正位以体言。大道以用言。盖既如此分开说。又须如此对勘说。意始圆。
上重庵先生(戊午)
宋高宗自奉币称臣之年。其失尊于虏金明矣。周赧汉献。自有其例。乌可一日虚冒大统之正乎。潭翁降统之论。诚不易也。但所与敌者。既是夷狄之猾夏者。而宋自是当日中国之主。其典章文物。犹存其旧。且况朝野之间。抗义斥和之论。尚有一脉未泯底阳意。则其在扶抑之义。又乌可直以丑虏之臣邦处之耶。愚意其纪年书法。当自失尊之年。变大书为细注。而犹得专系其元。而却附金年于圈下。以示中国之失尊。自中国之失尊。外夷之猾夏。自外夷之猾夏。其馀称帝书崩诏制幸行之类。直仍其旧。以及夫去臣正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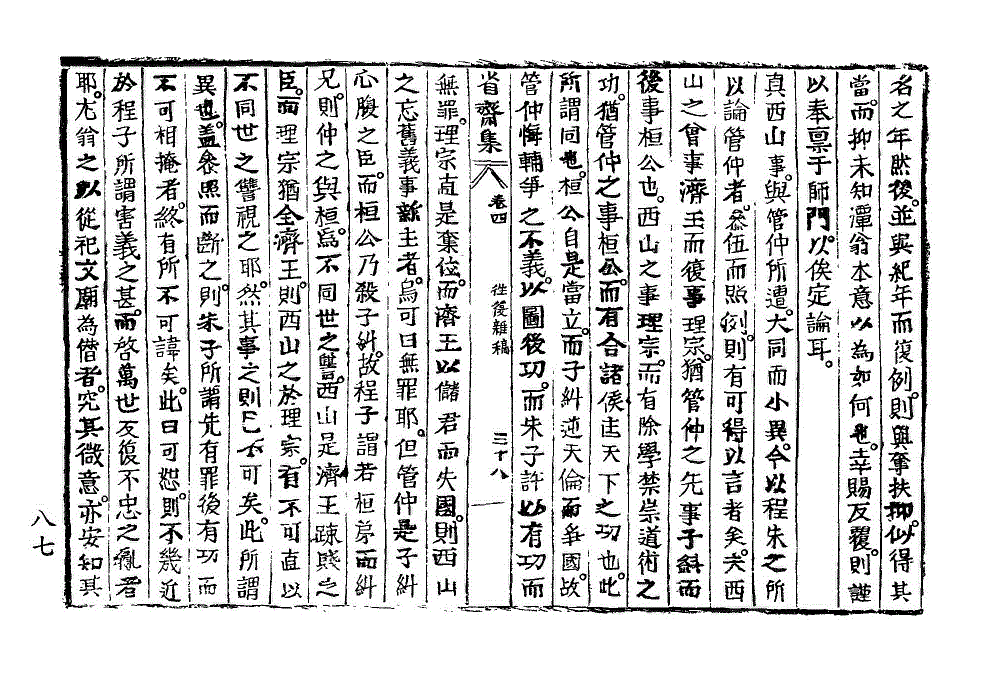 名之年然后。并与纪年而复例。则与夺扶抑。似得其当。而抑未知潭翁本意以为如何也。幸赐反覆。则谨以奉禀于师门。以俟定论耳。
名之年然后。并与纪年而复例。则与夺扶抑。似得其当。而抑未知潭翁本意以为如何也。幸赐反覆。则谨以奉禀于师门。以俟定论耳。真西山事。与管仲所遭。大同而小异。今以程朱之所以论管仲者。参伍而照例。则有可得以言者矣。夫西山之曾事济王而复事理宗。犹管仲之先事子纠而后事桓公也。西山之事理宗。而有除学禁崇道术之功。犹管仲之事桓公。而有合诸侯匡天下之功也。此所谓同也。桓公自是当立。而子纠逆天伦而争国。故管仲悔辅争之不义。以图后功。而朱子许以有功而无罪。理宗直是夺位。而济王以储君而失国。则西山之忘旧义事新主者。乌可曰无罪耶。但管仲是子纠心腹之臣。而桓公乃杀子纠。故程子谓若桓弟而纠兄。则仲之与桓。为不同世之雠。西山是济王疏贱之臣。而理宗犹全济王。则西山之于理宗。有不可直以不同世之雠视之耶。然其事之则已不可矣。此所谓异也。盖参照而断之。则朱子所谓先有罪后有功而不可相掩者。终有所不可讳矣。此曰可恕。则不几近于程子所谓害义之甚。而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者耶。尤翁之以从祀文庙为僭者。究其微意。亦安知其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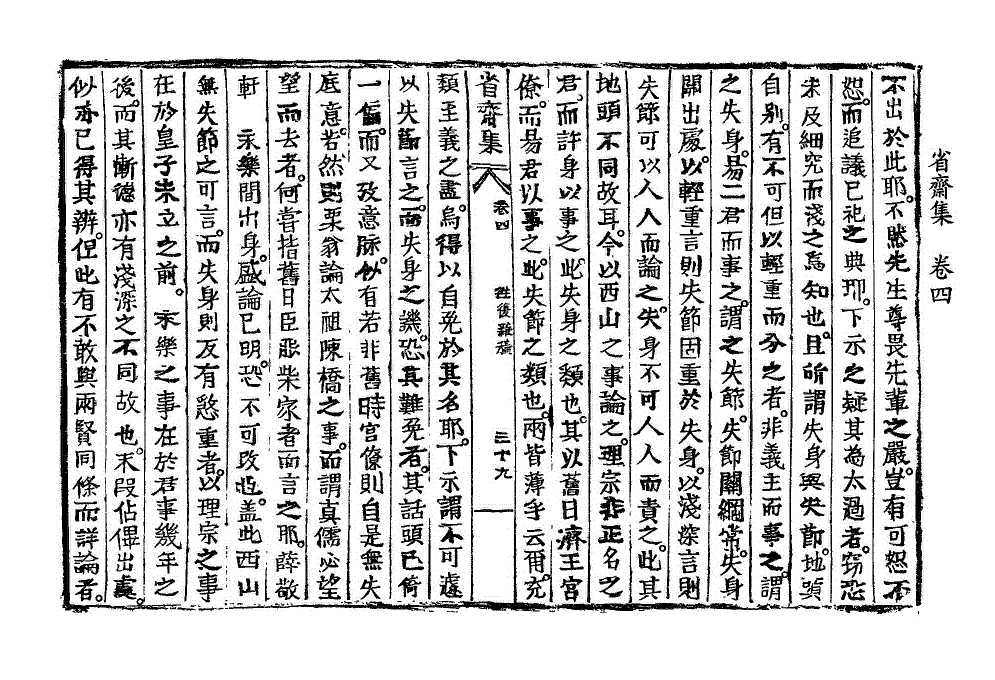 不出于此耶。不然先生尊畏先辈之严。岂有可恕不恕。而追议已祀之典耶。下示之疑其为太过者。窃恐未及细究而浅之为知也。且所谓失身与失节。地头自别。有不可但以轻重而分之者。非义主而事之。谓之失身。易二君而事之。谓之失节。失节关纲常。失身关出处。以轻重言则失节固重于失身。以浅深言则失节可以人人而论之。失身不可人人而责之。此其地头不同故耳。今以西山之事论之。理宗非正名之君。而许身以事之。此失身之类也。其以旧日济王宫僚。而易君以事之。此失节之类也。两皆薄乎云尔。充类至义之尽。乌得以自免于其名耶。下示谓不可遽以失节言之。而失身之讥。恐其难免者。其话头已倚一偏。而又考意脉。似有若非旧时宫僚则自是无失底意。若然则栗翁论太祖陈桥之事。而谓真儒必望望而去者。何尝指旧日臣服柴家者而言之耶。薛敬轩 永乐间出身。盛论已明。恐不可改也。盖此西山无失节之可言。而失身则反有煞重者。以理宗之事在于皇子未立之前。 永乐之事在于君事几年之后。而其惭德亦有浅深之不同故也。末段佔𠌫出处。似亦已得其辨。但此有不敢与两贤同条而详论者。
不出于此耶。不然先生尊畏先辈之严。岂有可恕不恕。而追议已祀之典耶。下示之疑其为太过者。窃恐未及细究而浅之为知也。且所谓失身与失节。地头自别。有不可但以轻重而分之者。非义主而事之。谓之失身。易二君而事之。谓之失节。失节关纲常。失身关出处。以轻重言则失节固重于失身。以浅深言则失节可以人人而论之。失身不可人人而责之。此其地头不同故耳。今以西山之事论之。理宗非正名之君。而许身以事之。此失身之类也。其以旧日济王宫僚。而易君以事之。此失节之类也。两皆薄乎云尔。充类至义之尽。乌得以自免于其名耶。下示谓不可遽以失节言之。而失身之讥。恐其难免者。其话头已倚一偏。而又考意脉。似有若非旧时宫僚则自是无失底意。若然则栗翁论太祖陈桥之事。而谓真儒必望望而去者。何尝指旧日臣服柴家者而言之耶。薛敬轩 永乐间出身。盛论已明。恐不可改也。盖此西山无失节之可言。而失身则反有煞重者。以理宗之事在于皇子未立之前。 永乐之事在于君事几年之后。而其惭德亦有浅深之不同故也。末段佔𠌫出处。似亦已得其辨。但此有不敢与两贤同条而详论者。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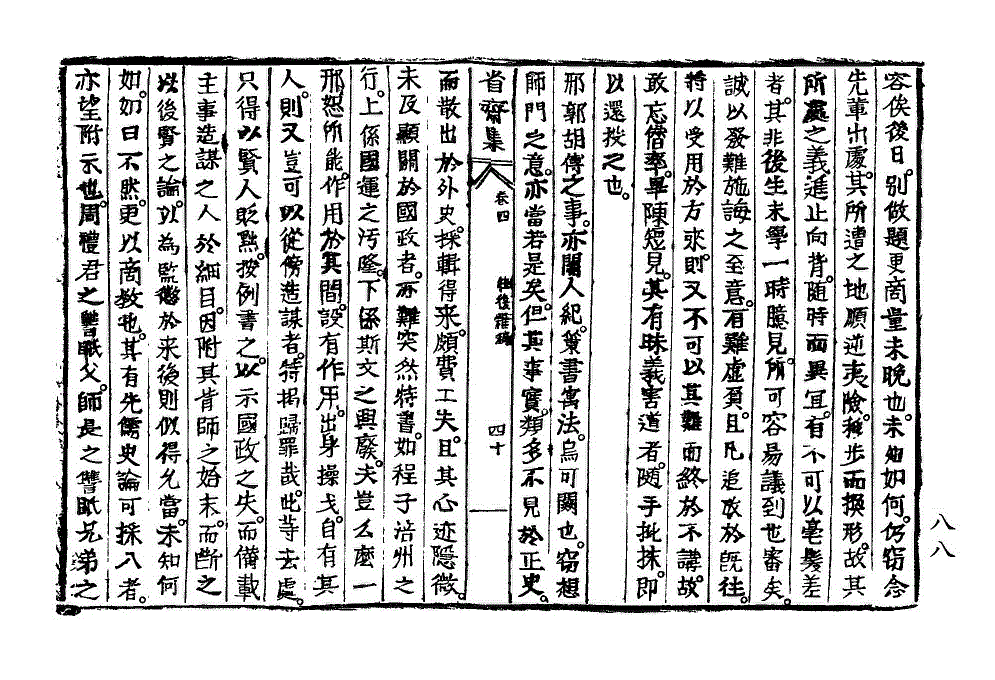 容俟后日。别做题更商量未晚也。未知如何。仍窃念先辈出处。其所遭之地顺逆夷险。移步而换形。故其所处之义进止向背。随时而异宜。有不可以毫发差者。其非后生末学一时臆见。所可容易议到也审矣。诚以发难施诲之至意。有难虚负。且凡追考于既往。将以受用于方来。则又不可以其难而终于不讲。故敢忘僭率。毕陈短见。其有昧义害道者。随手批抹。即以还投之也。
容俟后日。别做题更商量未晚也。未知如何。仍窃念先辈出处。其所遭之地顺逆夷险。移步而换形。故其所处之义进止向背。随时而异宜。有不可以毫发差者。其非后生末学一时臆见。所可容易议到也审矣。诚以发难施诲之至意。有难虚负。且凡追考于既往。将以受用于方来。则又不可以其难而终于不讲。故敢忘僭率。毕陈短见。其有昧义害道者。随手批抹。即以还投之也。邢郭胡傅之事。亦关人纪。策书寓法。乌可阙也。窃想师门之意。亦当若是矣。但其事实。类多不见于正史。而散出于外史。采辑得来。颇费工夫。且其心迹隐微。未及显关于国政者。亦难突然特书。如程子涪州之行。上系国运之污隆。下系斯文之兴废。夫岂幺么一邢恕所能。作用于其间。设有作用。出身操戈。自有其人。则又岂可以从傍造谋者。特揭归罪哉。此等去处。只得以贤人贬黜。按例书之。以示国政之失。而备载主事造谋之人于细目。因附其背师之始末。而断之以后贤之论。以为监惩于来后则似得允当。未知何如。如曰不然。更以商教也。其有先儒史论可采入者。亦望附示也。周礼君之雠视父。师长之雠视兄弟之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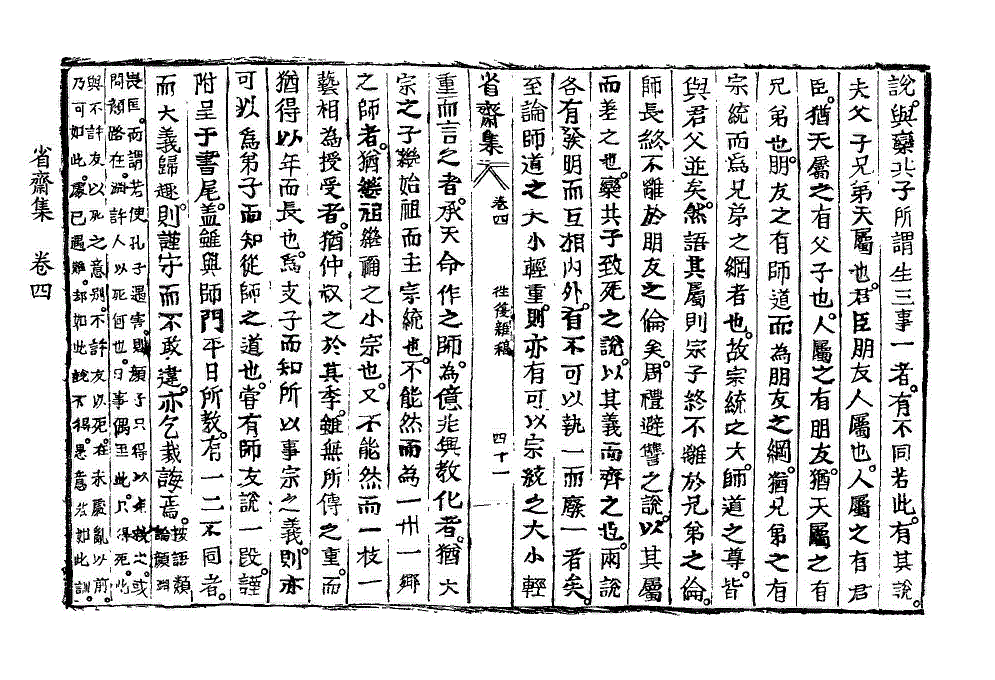 说。与栾共子所谓生三事一者。有不同若此。有其说。夫父子兄弟天属也。君臣朋友人属也。人属之有君臣。犹天属之有父子也。人属之有朋友。犹天属之有兄弟也。朋友之有师道而为朋友之纲。犹兄弟之有宗统而为兄弟之纲者也。故宗统之大。师道之尊。皆与君父并矣。然语其属则宗子终不离于兄弟之伦。师长终不离于朋友之伦矣。周礼避雠之说。以其属而差之也。栾共子致死之说。以其义而齐之也。两说各有发明而互相内外。有不可以执一而废一者矣。至论师道之大小轻重。则亦有可以宗统之大小轻重而言之者。承天命作之师。为亿兆兴教化者。犹大宗之子继始祖而主宗统也。不能然而为一州一乡之师者。犹继祖继祢之小宗也。又不能然而一技一艺相为授受者。犹仲叔之于其季。虽无所传之重。而犹得以年而长也。为支子而知所以事宗之义。则亦可以为弟子而知从师之道也。尝有师友说一段。谨附呈于书尾。盖虽与师门平日所教。有一二不同者。而大义归趣。则谨守而不敢违。亦乞裁诲焉。(按语类论颜渊畏匡。而谓若使孔子遇害。则颜子只得以死救之。或问颜路在。渊许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与不许友以死之意别。不许友以死。在未处乱以前。乃可如此。处已遇难。却如此说不得。愚意若如此训。
说。与栾共子所谓生三事一者。有不同若此。有其说。夫父子兄弟天属也。君臣朋友人属也。人属之有君臣。犹天属之有父子也。人属之有朋友。犹天属之有兄弟也。朋友之有师道而为朋友之纲。犹兄弟之有宗统而为兄弟之纲者也。故宗统之大。师道之尊。皆与君父并矣。然语其属则宗子终不离于兄弟之伦。师长终不离于朋友之伦矣。周礼避雠之说。以其属而差之也。栾共子致死之说。以其义而齐之也。两说各有发明而互相内外。有不可以执一而废一者矣。至论师道之大小轻重。则亦有可以宗统之大小轻重而言之者。承天命作之师。为亿兆兴教化者。犹大宗之子继始祖而主宗统也。不能然而为一州一乡之师者。犹继祖继祢之小宗也。又不能然而一技一艺相为授受者。犹仲叔之于其季。虽无所传之重。而犹得以年而长也。为支子而知所以事宗之义。则亦可以为弟子而知从师之道也。尝有师友说一段。谨附呈于书尾。盖虽与师门平日所教。有一二不同者。而大义归趣。则谨守而不敢违。亦乞裁诲焉。(按语类论颜渊畏匡。而谓若使孔子遇害。则颜子只得以死救之。或问颜路在。渊许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与不许友以死之意别。不许友以死。在未处乱以前。乃可如此。处已遇难。却如此说不得。愚意若如此训。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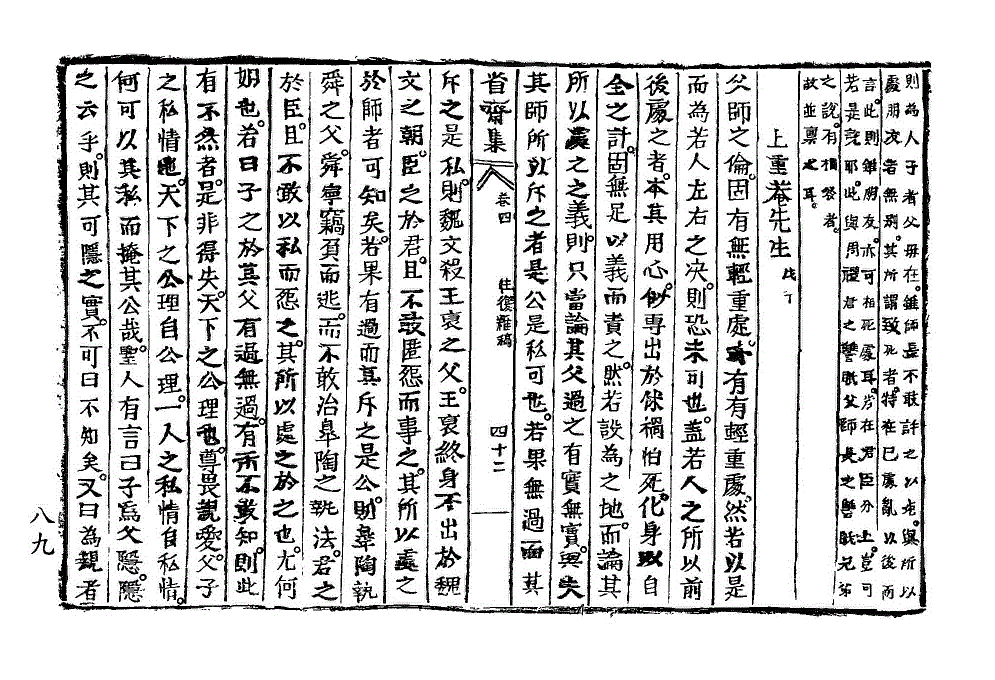 则为人子者父母在。虽师长不敢许之以死。与所以处朋友者无别。其所谓致死者。特在已处乱以后而言。此则虽朋友。亦可相死处耳。若在君臣分上。岂可若是说耶。此与周礼君之雠视父师长之雠视兄弟之说。有相发者。故并禀之耳。)
则为人子者父母在。虽师长不敢许之以死。与所以处朋友者无别。其所谓致死者。特在已处乱以后而言。此则虽朋友。亦可相死处耳。若在君臣分上。岂可若是说耶。此与周礼君之雠视父师长之雠视兄弟之说。有相发者。故并禀之耳。)上重庵先生(戊午)
父师之伦。固有无轻重处。亦有有轻重处。然若以是而为若人左右之决。则恐未可也。盖若人之所以前后处之者。本其用心。似专出于怵祸怕死。化身以自全之计。固无足以义而责之。然若设为之地。而论其所以处之之义。则只当论其父过之有实无实。与夫其师所以斥之者是公是私可也。若果无过而其斥之是私。则魏文杀王裒之父。王裒终身不出于魏文之朝。臣之于君。且不敢匿怨而事之。其所以处之于师者可知矣。若果有过而其斥之是公。则皋陶执舜之父。舜宁窃负而逃。而不敢治皋陶之执法。君之于臣。且不敢以私而怨之。其所以处之于之也。尤何如也。若曰子之于其父有过无过。有所不敢知。则此有不然者。是非得失。天下之公理也。尊畏亲爱。父子之私情也。天下之公理自公理。一人之私情自私情。何可以其私而掩其公哉。圣人有言曰子为父隐。隐之云乎。则其可隐之实。不可曰不知矣。又曰为亲者
省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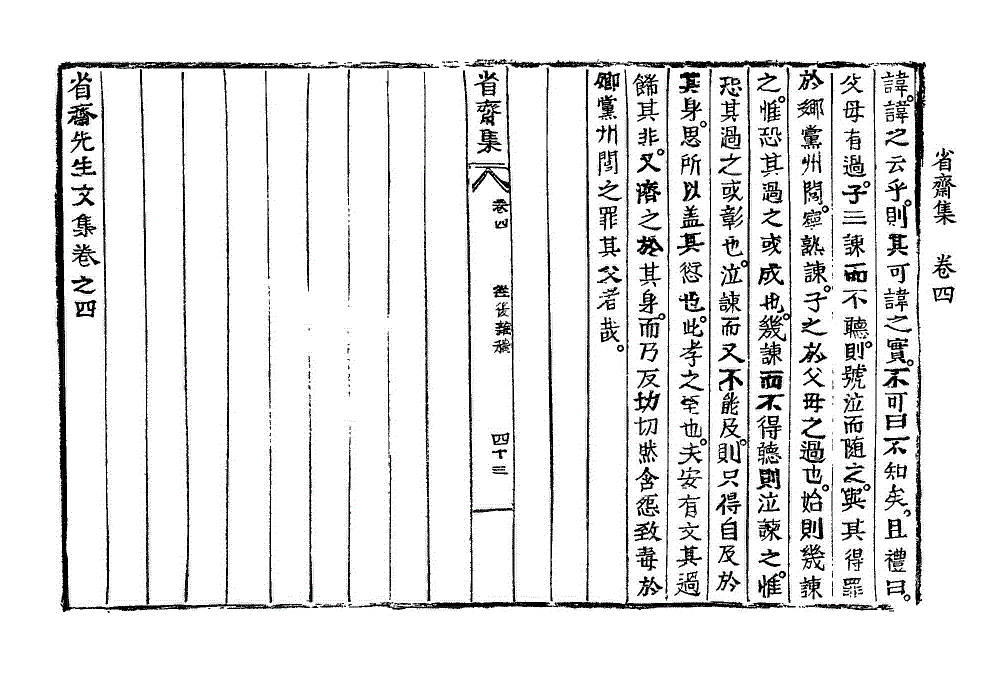 讳。讳之云乎。则其可讳之实。不可曰不知矣。且礼曰。父母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子之于父母之过也。始则几谏之。惟恐其过之或成也。几谏而不得听则泣谏之。惟恐其过之或彰也。泣谏而又不能及。则只得自及于其身。思所以盖其愆也。此孝之至也。夫安有文其过饰其非。又济之于其身。而乃反切切然含怨致毒于乡党州闾之罪其父者哉。
讳。讳之云乎。则其可讳之实。不可曰不知矣。且礼曰。父母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子之于父母之过也。始则几谏之。惟恐其过之或成也。几谏而不得听则泣谏之。惟恐其过之或彰也。泣谏而又不能及。则只得自及于其身。思所以盖其愆也。此孝之至也。夫安有文其过饰其非。又济之于其身。而乃反切切然含怨致毒于乡党州闾之罪其父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