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x 页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记
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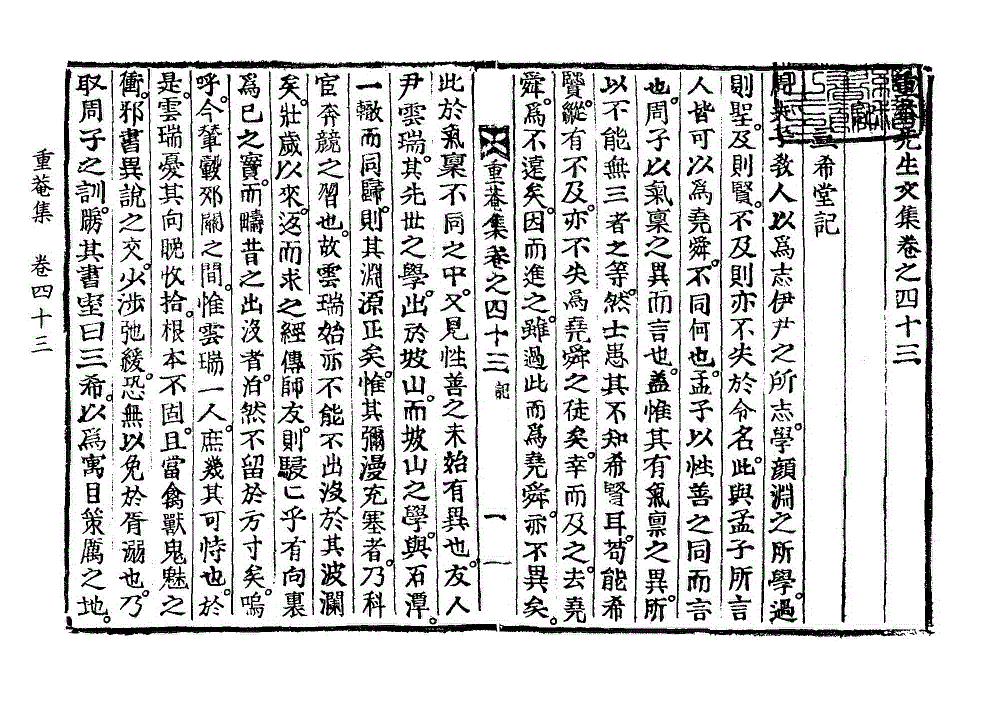 三希堂记
三希堂记周夫子教人以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此与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不同何也。孟子以性善之同而言也。周子以气禀之异而言也。盖惟其有气禀之异。所以不能无三者之等。然士患其不知希贤耳。苟能希贤。纵有不及。亦不失为尧舜之徒矣。幸而及之。去尧舜。为不远矣。因而进之。虽过此而为尧舜。亦不异矣。此于气禀不同之中。又见性善之未始有异也。友人尹云瑞。其先世之学。出于坡山。而坡山之学。与石潭。一辙而同归。则其渊源正矣。惟其弥漫充塞者。乃科宦奔竞之习也。故云瑞始亦不能不出没于其波澜矣。壮岁以来。返而求之经传师友。则骎骎乎有向里为己之实。而畴昔之出没者。泊然不留于方寸矣。呜呼。今辇毂郊关之间。惟云瑞一人。庶几其可恃也。于是。云瑞忧其向晚收拾。根本不固。且当禽兽鬼魅之冲。邪书异说之交。少涉弛缓。恐无以免于胥溺也。乃取周子之训。榜其书室曰三希。以为寓目策厉之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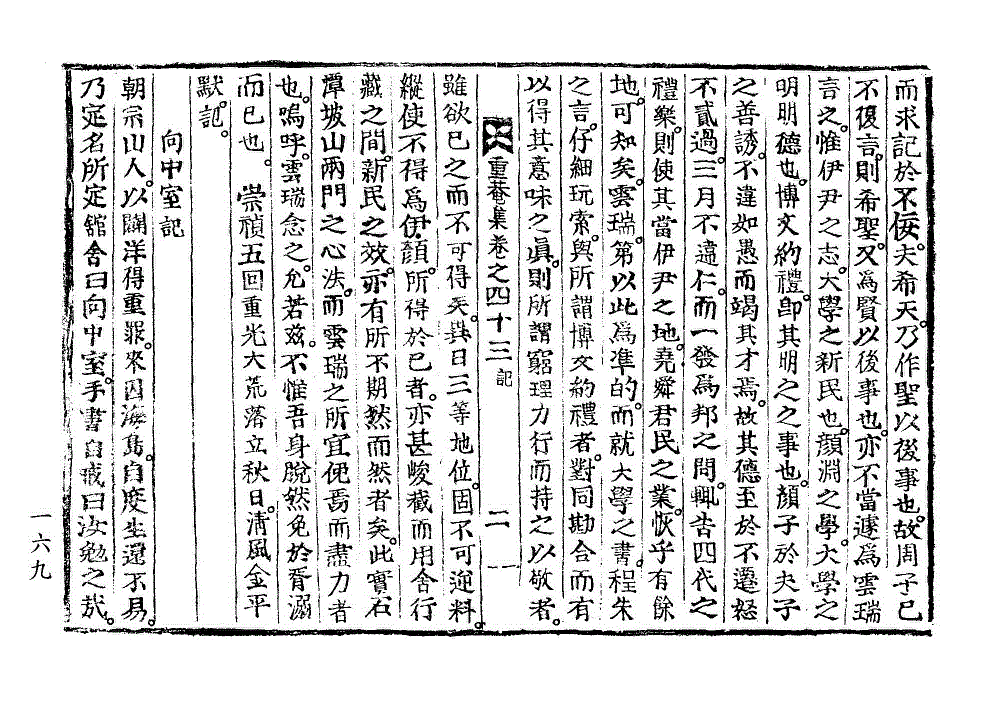 而求记于不佞。夫希天。乃作圣以后事也。故周子已不复言。则希圣。又为贤以后事也。亦不当遽为云瑞言之。惟伊尹之志。大学之新民也。颜渊之学。大学之明明德也。博文约礼。即其明之之事也。颜子于夫子之善诱。不违如愚而竭其才焉。故其德至于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而一发为邦之问。辄告四代之礼乐。则使其当伊尹之地。尧舜君民之业。恢乎有馀地。可知矣。云瑞。第以此为准的。而就大学之书。程朱之言。仔细玩索。与所谓博文约礼者。对同勘合而有以得其意味之真。则所谓穷理力行而持之以敬者。虽欲已之而不可得矣。异日三等地位。固不可逆料。纵使不得为伊,颜。所得于己者。亦甚峻截而用舍行藏之间。新民之效。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实石潭坡山两门之心法。而云瑞之所宜俛焉而尽力者也。呜呼。云瑞念之。允若玆。不惟吾身脱然免于胥溺而已也 崇祯五回重光大荒落立秋日。清风金平默。记。
而求记于不佞。夫希天。乃作圣以后事也。故周子已不复言。则希圣。又为贤以后事也。亦不当遽为云瑞言之。惟伊尹之志。大学之新民也。颜渊之学。大学之明明德也。博文约礼。即其明之之事也。颜子于夫子之善诱。不违如愚而竭其才焉。故其德至于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而一发为邦之问。辄告四代之礼乐。则使其当伊尹之地。尧舜君民之业。恢乎有馀地。可知矣。云瑞。第以此为准的。而就大学之书。程朱之言。仔细玩索。与所谓博文约礼者。对同勘合而有以得其意味之真。则所谓穷理力行而持之以敬者。虽欲已之而不可得矣。异日三等地位。固不可逆料。纵使不得为伊,颜。所得于己者。亦甚峻截而用舍行藏之间。新民之效。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实石潭坡山两门之心法。而云瑞之所宜俛焉而尽力者也。呜呼。云瑞念之。允若玆。不惟吾身脱然免于胥溺而已也 崇祯五回重光大荒落立秋日。清风金平默。记。向中室记
朝宗山人。以辟洋得重罪。来囚海岛。自度生还不易。乃定名所定馆舍曰向中室。手书自戒曰汝勉之哉。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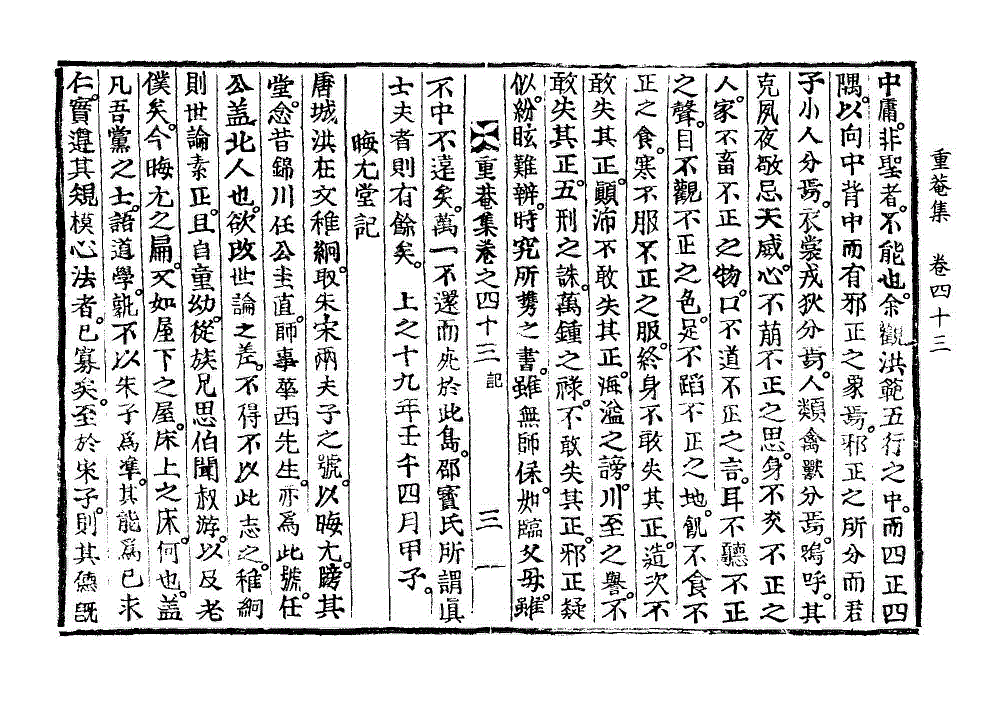 中庸。非圣者。不能也。余观洪范五行之中。而四正四隅。以向中背中而有邪正之象焉。邪正之所分而君子小人分焉。衣裳戎狄分焉。人类禽兽分焉。呜呼。其克夙夜敬忌天威。心不萌不正之思。身不交不正之人。家不畜不正之物。口不道不正之言。耳不听不正之声。目不观不正之色。足不蹈不正之地。饥不食不正之食。寒不服不正之服。终身不敢失其正。造次不敢失其正。颠沛不敢失其正。海溢之谤。川至之誉。不敢失其正。五刑之诛。万钟之禄。不敢失其正。邪正疑似。纷眩难辨。时究所携之书。虽无师保。如临父母。虽不中不远矣。万一不还而死于此岛。邵宝氏所谓真士夫者则有馀矣。 上之十九年壬午四月甲子。
中庸。非圣者。不能也。余观洪范五行之中。而四正四隅。以向中背中而有邪正之象焉。邪正之所分而君子小人分焉。衣裳戎狄分焉。人类禽兽分焉。呜呼。其克夙夜敬忌天威。心不萌不正之思。身不交不正之人。家不畜不正之物。口不道不正之言。耳不听不正之声。目不观不正之色。足不蹈不正之地。饥不食不正之食。寒不服不正之服。终身不敢失其正。造次不敢失其正。颠沛不敢失其正。海溢之谤。川至之誉。不敢失其正。五刑之诛。万钟之禄。不敢失其正。邪正疑似。纷眩难辨。时究所携之书。虽无师保。如临父母。虽不中不远矣。万一不还而死于此岛。邵宝氏所谓真士夫者则有馀矣。 上之十九年壬午四月甲子。晦尤堂记
唐城洪在文稚絅。取朱宋两夫子之号。以晦尤。榜其堂。念昔锦川任公圭直。师事华西先生。亦为此号。任公盖北人也。欲改世论之差。不得不以此志之。稚絅则世论素正。且自童幼。从族兄思伯闻叔游。以及老仆矣。今晦尤之扁。又如屋下之屋。床上之床。何也。盖凡吾党之士。语道学。孰不以朱子为准。其能为己求仁。实遵其规模心法者。已寡矣。至于宋子。则其德既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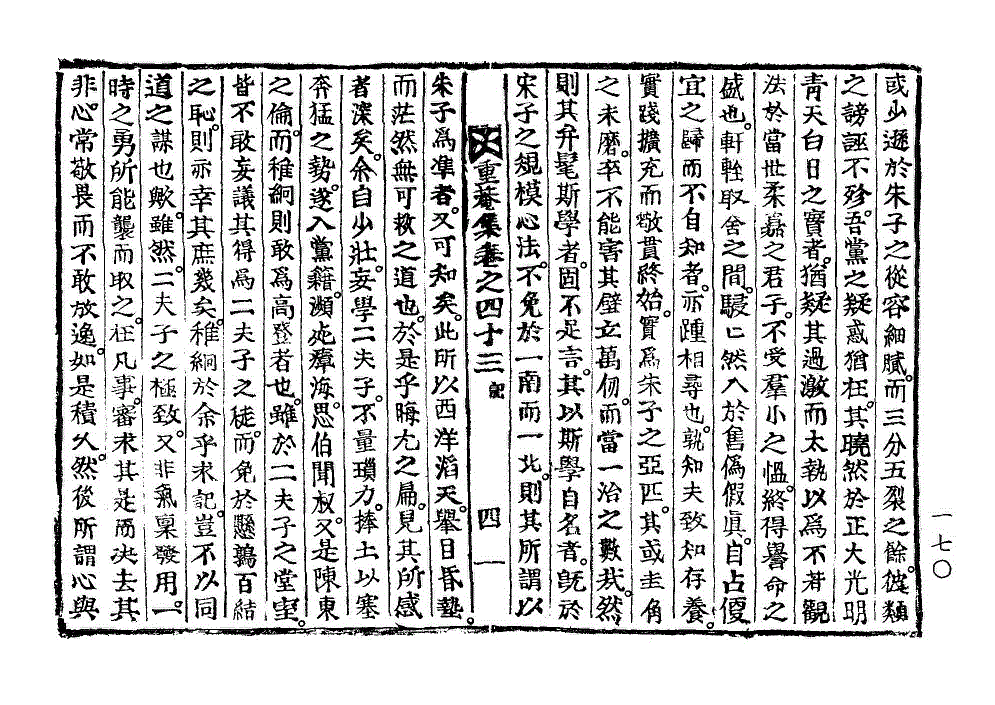 或少逊于朱子之从容细腻。而三分五裂之馀。彼类之谤诬不殄。吾党之疑惑犹在。其晓然于正大光明青天白日之实者。犹疑其过激而太执以为不若观法于当世柔嘉之君子。不受群小之愠。终得誉命之盛也。轩轾取舍之间。骎骎然入于售伪假真。自占便宜之归而不自知者。亦踵相寻也。孰知夫致知存养。实践扩充而敬贯终始。实为朱子之亚匹。其或圭角之未磨。卒不能害其壁立万仞。而当一治之数哉。然则其弁髦斯学者。固不足言。其以斯学自名者。既于宋子之规模心法。不免于一南而一北。则其所谓以朱子为准者。又可知矣。此所以西洋滔天。举目昏垫。而茫然无可救之道也。于是乎晦尤之扁。见其所感者深矣。余自少壮。妄学二夫子。不量琐力。捧土以塞奔猛之势。遂入党籍。濒死瘴海。思伯闻叔。又是陈东之伦。而稚絅则敢为高登者也。虽于二夫子之堂室。皆不敢妄议其得为二夫子之徒。而免于悬鹑百结之耻。则亦幸其庶几矣。稚絅于余乎求记。岂不以同道之谋也欤。虽然。二夫子之极致。又非气禀发用。一时之勇所能袭而取之。在凡事。审求其是而决去其非。心常敬畏而不敢放逸。如是积久。然后所谓心与
或少逊于朱子之从容细腻。而三分五裂之馀。彼类之谤诬不殄。吾党之疑惑犹在。其晓然于正大光明青天白日之实者。犹疑其过激而太执以为不若观法于当世柔嘉之君子。不受群小之愠。终得誉命之盛也。轩轾取舍之间。骎骎然入于售伪假真。自占便宜之归而不自知者。亦踵相寻也。孰知夫致知存养。实践扩充而敬贯终始。实为朱子之亚匹。其或圭角之未磨。卒不能害其壁立万仞。而当一治之数哉。然则其弁髦斯学者。固不足言。其以斯学自名者。既于宋子之规模心法。不免于一南而一北。则其所谓以朱子为准者。又可知矣。此所以西洋滔天。举目昏垫。而茫然无可救之道也。于是乎晦尤之扁。见其所感者深矣。余自少壮。妄学二夫子。不量琐力。捧土以塞奔猛之势。遂入党籍。濒死瘴海。思伯闻叔。又是陈东之伦。而稚絅则敢为高登者也。虽于二夫子之堂室。皆不敢妄议其得为二夫子之徒。而免于悬鹑百结之耻。则亦幸其庶几矣。稚絅于余乎求记。岂不以同道之谋也欤。虽然。二夫子之极致。又非气禀发用。一时之勇所能袭而取之。在凡事。审求其是而决去其非。心常敬畏而不敢放逸。如是积久。然后所谓心与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1H 页
 理一者。可得而言也。此又二夫子临箦之要诀也。稚絅请更从事于斯焉。 崇祯五癸未暮春。智海累人。
理一者。可得而言也。此又二夫子临箦之要诀也。稚絅请更从事于斯焉。 崇祯五癸未暮春。智海累人。明月楼记
智洲镇西。新构谪舍。爰居爰处。厥既有日。具君士正与馆人。就室东檐。加设小楼。工讫。出户而坐。明月时至。清爽满襟。庚热退伏。于是。馆人进酒。士正乘醺。展纸以口笔。榜曰明月。而揭之楣。余因是而有感焉。月太阴之精也。轮郭至虚。故受大阳之光。而无纤毫以贰之。明足以代日。而容光无不照矣。人君知此。则可以虚受天下之善。而德业日起矣。学者知此。则可以虚受师友之益。而道义日进矣。虚之如何。寡欲而已。寡之如何。居敬而已。寡之又寡。则此心无物。敬之又敬。则此心常存。虚以受人。莫要于此矣。噫。粤瞻枫宸。云天缥缈。芹曝之献。吾知其已矣。吾与士正。以此相勖于坎窞之中。为朝闻夕死之地。则虽百欧洲。莫之能御也。易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如此。胸中洒落。霁月扬辉。虽以匹夫之微。处石藜之困。不害其将照四国也。舍乎此则欲蔽心昏。虚骄自贤。随其所在。失则而入地。无可救之方矣。吁。不亦危哉殆哉。既以此相戒。遂书以为记。时 崇祯纪元五癸未六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1L 页
 月既望也。
月既望也。智岛凤凰峰记
朝鲜之南海。有智岛。峰峦厜㕒。环数十里。至于镇北。耸然而起者。居人所称凤凰峰也。按说文。凤凰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见则天下安宁。飞则群鸟从以万数。夫朝鲜。天下之东也。帝出于震矣。日出于卯矣。元长乎万善矣。仁包乎四德矣。洛书三祥之所在矣。殷师彝伦之所叙矣。君子之国。非此而谁欤。然则仪于舜韶。鸣于文岐。嗈嗈喈喈于卷阿之时。岂或产之于此而见之于彼者欤。惜乎。卫满以后。坏乱相因。载籍扫尽。虽殷师之政教。有不足徵。况于其馀乎。噫。舜文成周。忽焉没矣。彼龙文龟背。和气之所钟。汉唐宋明之盛。邈然无影响者。宁可以想像其彷佛也耶。抑或偶然生出。无梧桐之可栖。无竹实之可食。枳棘之所塞。蹄迹之所交。鬼魅之所凌。矰缴之所设。万数之从。将亦色举。则将无同于鲁麟之踣乎。虽深藏。且恐不免。况影响稍露乎。是其不生也宜哉。呜呼。岂惟凤凰。人事亦有然者。遂感而书之。 崇祯五甲申林钟下浣。镇下累人。
聿脩斋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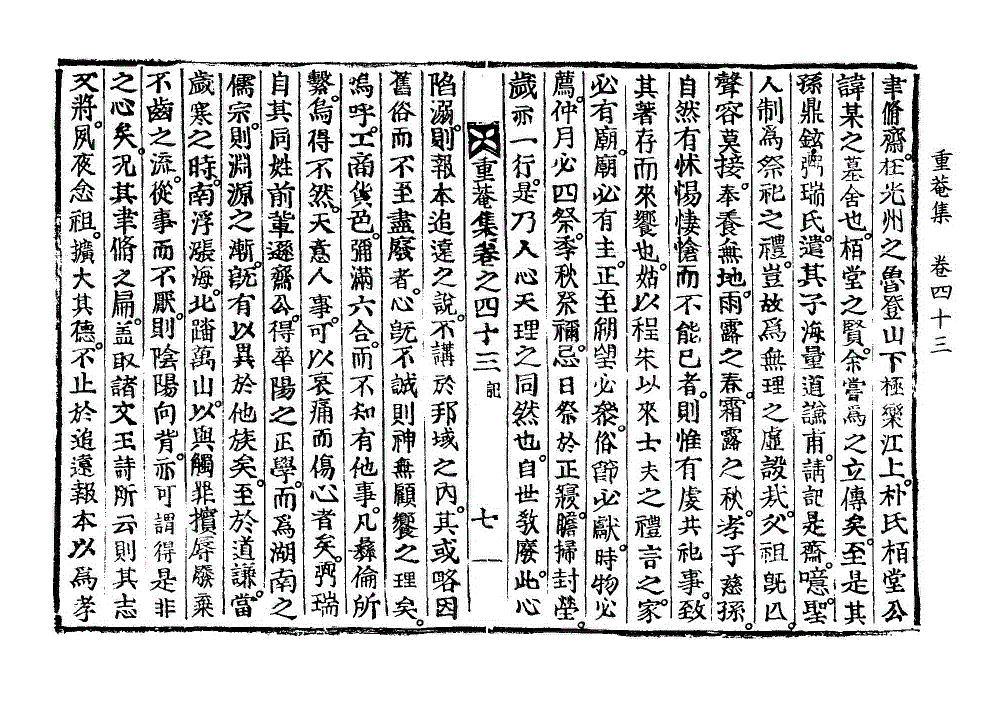 聿脩斋。在光州之鲁登山下极乐江上。朴氏柏堂公讳某之墓舍也。柏堂之贤。余尝为之立传矣。至是其孙鼎铉,弼瑞氏。遣其子海量道谦甫。请记是斋。噫。圣人制为祭祀之礼。岂故为无理之虚设哉。父祖既亡。声容莫接。奉养无地。雨露之春。霜露之秋。孝子慈孙。自然有怵惕悽怆而不能已者。则惟有虔共祀事。致其著存而来飨也。姑以程朱以来士夫之礼言之。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正至朔望必参。俗节必献。时物必荐。仲月必四祭。季秋祭祢。忌日祭于正寝。瞻扫封茔。岁亦一行。是乃人心天理之同然也。自世教废。此心陷溺。则报本追远之说。不讲于邦域之内。其或略因旧俗而不至尽废者。心既不诚则神无顾飨之理矣。呜呼。工商货色。弥满六合。而不知有他事。凡彝伦所系。乌得不然。天意人事。可以哀痛而伤心者矣。弼瑞自其同姓前辈逊斋公。得华阳之正学。而为湖南之儒宗。则渊源之渐。既有以异于他族矣。至于道谦。当岁寒之时。南浮涨海。北踏万山。以与触罪摈辱废弃不齿之流。从事而不厌。则阴阳向背。亦可谓得是非之心矣。况其聿脩之扁。盖取诸文王诗所云则其志又将。夙夜念祖。扩大其德。不止于追远报本以为孝
聿脩斋。在光州之鲁登山下极乐江上。朴氏柏堂公讳某之墓舍也。柏堂之贤。余尝为之立传矣。至是其孙鼎铉,弼瑞氏。遣其子海量道谦甫。请记是斋。噫。圣人制为祭祀之礼。岂故为无理之虚设哉。父祖既亡。声容莫接。奉养无地。雨露之春。霜露之秋。孝子慈孙。自然有怵惕悽怆而不能已者。则惟有虔共祀事。致其著存而来飨也。姑以程朱以来士夫之礼言之。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正至朔望必参。俗节必献。时物必荐。仲月必四祭。季秋祭祢。忌日祭于正寝。瞻扫封茔。岁亦一行。是乃人心天理之同然也。自世教废。此心陷溺。则报本追远之说。不讲于邦域之内。其或略因旧俗而不至尽废者。心既不诚则神无顾飨之理矣。呜呼。工商货色。弥满六合。而不知有他事。凡彝伦所系。乌得不然。天意人事。可以哀痛而伤心者矣。弼瑞自其同姓前辈逊斋公。得华阳之正学。而为湖南之儒宗。则渊源之渐。既有以异于他族矣。至于道谦。当岁寒之时。南浮涨海。北踏万山。以与触罪摈辱废弃不齿之流。从事而不厌。则阴阳向背。亦可谓得是非之心矣。况其聿脩之扁。盖取诸文王诗所云则其志又将。夙夜念祖。扩大其德。不止于追远报本以为孝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2L 页
 也。呜呼。审如是。蹄迹之交。伥鬼之恣。终亦有可制之道矣。吾且引领南向而望其日进于高远也。遂书以还之。 永历四乙酉重阳节。清城金平默。记。
也。呜呼。审如是。蹄迹之交。伥鬼之恣。终亦有可制之道矣。吾且引领南向而望其日进于高远也。遂书以还之。 永历四乙酉重阳节。清城金平默。记。坦斋记
友人沈稚浚书室。无扁楣。申恳于余。余取履卦九二之辞。命名曰坦斋。稚浚曰。有说乎。曰。履之九二。刚中在下。无应于上。履道平坦。幽人守贞之象也。稚浚少治功令。见欧罗得志。六合昏濛。遂绝迹城府。息影衡泌。余自智海放归。寓白云山中。距坦斋一里而近。稚浚率塾中冠童而从之。课洛闽之书。习洙泗之礼。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谁复适从。求为幽人而已矣。虽然。汉儒有言。无德而隐。谓之素隐。以其在我者。未有刚中之德。徒以无应而止。强名为幽人耳。今稚浚与二三子。涧饮木食。而从事于洙泗,洛闽之旧。则虽谓之皎皎乎霞外。亭亭乎物表可也。然其所课所习。人道之体用备矣。如或循例托名。贰以二。参以三。而卒焉无得于道妙。则所履者依旧是世俗之陋。幸而粗见其一二。朱子所谓困善而无精采。履之也艰苦生涩。而不见其坦然。则顾眄之间。利害之所迫。其中必乱而所守不保其贞固矣。幽人之名。岂不卒为素隐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3H 页
 之归哉。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主一无适。思学相资。不以寒饿而改。不以劳苦而弛。不以毁誉而动。课习之久。而明善诚身之功。日以至焉。则日用之间。道体呈露。坦然履之。无复艰苦生涩之患矣。至是而所谓坦荡荡。心广体胖者。为吾人之状德语也。如此则中不自乱而无愧于古之幽人矣。呜呼。朱子不云乎。百尺竿头。进取一步。盍相与勉旃。稚浚请书以为记。力疾塞命。㱡㱡焉不成章。可覆瓿也。 永历五丁亥仲吕上弦。清城金平默。记。
之归哉。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主一无适。思学相资。不以寒饿而改。不以劳苦而弛。不以毁誉而动。课习之久。而明善诚身之功。日以至焉。则日用之间。道体呈露。坦然履之。无复艰苦生涩之患矣。至是而所谓坦荡荡。心广体胖者。为吾人之状德语也。如此则中不自乱而无愧于古之幽人矣。呜呼。朱子不云乎。百尺竿头。进取一步。盍相与勉旃。稚浚请书以为记。力疾塞命。㱡㱡焉不成章。可覆瓿也。 永历五丁亥仲吕上弦。清城金平默。记。云潭精舍记
榜曰云潭精舍者。前南瀛罪累人。任便居住之所也。在武夷洞口居然台之东北数十武。曩自澄波。东入于此。台记详之。诸生当暑月。讲习于台上。寒节择洞人外舍。迭就而会之。则事多不便矣。明年春。人忘乌昧。众议鸠财。敦事月馀。突兀眼前。数十人以上。恢然可容也。噫。 圣上畴昔之 谴。迫于时议之向背。黾勉而为之耳。毕竟 圣意以诵法洙泗洛闽。使三纲五常不坠地。而盖其罪。不至屏裔而死。故宽假之。使得优游自适于千岩万壑之中。而不复问焉。则就木之前。谨当奉承微意。收拾散魄。燖温故学。以与生徒。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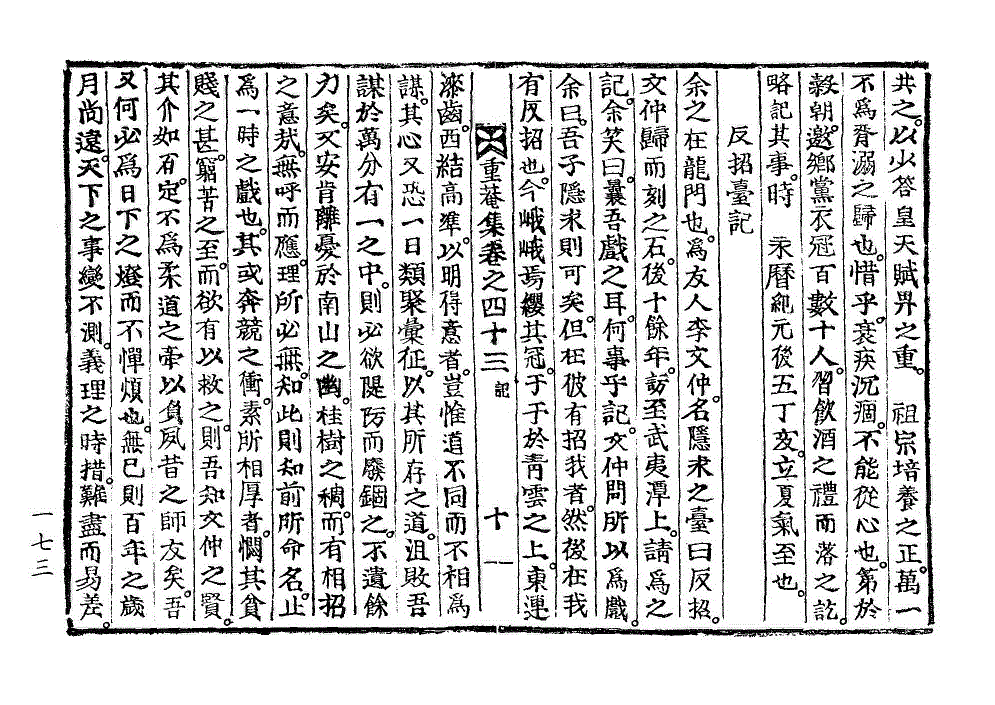 共之。以少答皇天赋畀之重。 祖宗培养之正。万一不为胥溺之归也。惜乎。衰疾沉痼。不能从心也。第于谷朝。邀乡党衣冠百数十人。习饮酒之礼而落之讫。略记其事。时 永历纪元后五丁亥。立夏气至也。
共之。以少答皇天赋畀之重。 祖宗培养之正。万一不为胥溺之归也。惜乎。衰疾沉痼。不能从心也。第于谷朝。邀乡党衣冠百数十人。习饮酒之礼而落之讫。略记其事。时 永历纪元后五丁亥。立夏气至也。反招台记
余之在龙门也。为友人李文仲。名隐求之台曰反招。文仲归而刻之石。后十馀年。访至武夷潭上。请为之记。余笑曰。曩吾戏之耳。何事乎记。文仲问所以为戏。余曰。吾子隐求则可矣。但在彼有招我者。然后在我有反招也。今峨峨焉缨其冠。于于于青云之上。东连漆齿。西结高准。以明得意者。岂惟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其心又恐一日类聚汇征。以其所存之道。沮败吾谋于万分有一之中。则必欲堤防而废锢之。不遗馀力矣。又安肯离忧于南山之幽。桂树之稠。而有相招之意哉。无呼而应。理所必无。知此则知前所命名。止为一时之戏也。其或奔竞之冲。素所相厚者。悯其贫贱之甚。穷苦之至。而欲有以救之。则吾知文仲之贤。其介如石。定不为柔道之牵以负夙昔之师友矣。吾又何必为日下之灯而不惮烦也。无已则百年之岁月尚远。天下之事变不测。义理之时措。难尽而易差。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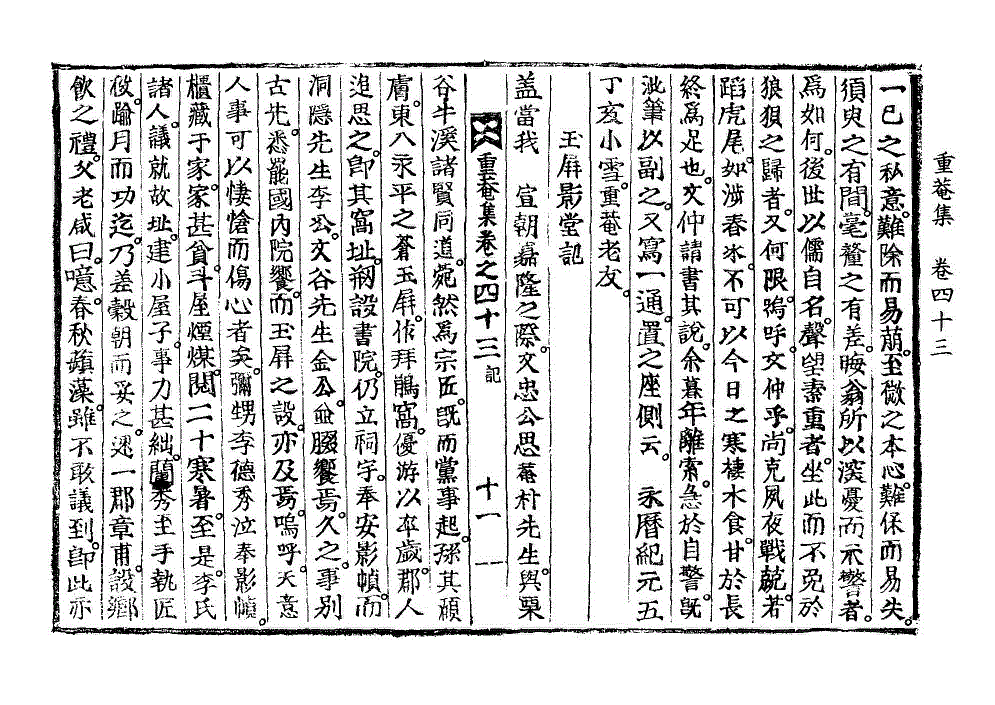 一己之私意。难除而易萌。至微之本心。难保而易失。须臾之有间。毫釐之有差。晦翁所以深忧而示警者。为如何。后世以儒自名。声望素重者。坐此而不免于狼狈之归者。又何限。呜呼。文仲乎。尚克夙夜战兢。若蹈虎尾。如涉春冰。不可以今日之寒栖木食。甘于长终为足也。文仲请书其说。余暮年离索。急于自警。既泚笔以副之。又写一通。置之座侧云。 永历纪元五丁亥小雪。重庵老友。
一己之私意。难除而易萌。至微之本心。难保而易失。须臾之有间。毫釐之有差。晦翁所以深忧而示警者。为如何。后世以儒自名。声望素重者。坐此而不免于狼狈之归者。又何限。呜呼。文仲乎。尚克夙夜战兢。若蹈虎尾。如涉春冰。不可以今日之寒栖木食。甘于长终为足也。文仲请书其说。余暮年离索。急于自警。既泚笔以副之。又写一通。置之座侧云。 永历纪元五丁亥小雪。重庵老友。玉屏影堂记
盖当我 宣朝嘉隆之际。文忠公思庵朴先生。与栗谷,牛溪诸贤同道。菀然为宗匠。既而党事起。孙其硕肤。东入永平之苍玉屏。作拜鹃窝。优游以卒岁。郡人追思之。即其窝址。刱设书院。仍立祠宇。奉安影帧。而洞隐先生李公。文谷先生金公。并啜飨焉。久之。事别古先。悉罢国内院飨。而玉屏之设。亦及焉。呜呼。天意人事可以悽怆而伤心者矣。弥甥李德秀泣奉影帧。匮藏于家。家甚贫。斗屋烟煤。阅二十寒暑。至是。李氏诸人。议就故址。建小屋子。事力甚绌。兰秀至手执匠役。踰月而功迄。乃差谷朝而妥之。速一郡章甫。设乡饮之礼。父老咸曰。噫。春秋蘋藻。虽不敢议到。即此亦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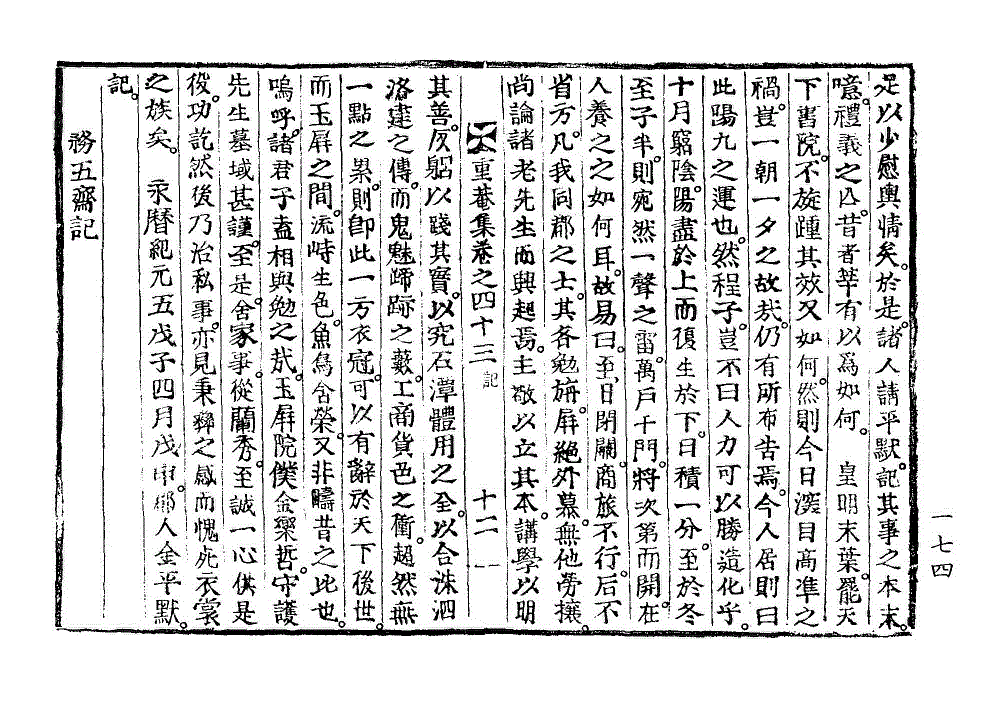 足以少慰舆情矣。于是。诸人请平默。记其事之本末。噫。礼义之亡。昔者莘有以为如何。 皇明末叶。罢天下书院。不旋踵其效又如何。然则今日深目高准之祸。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仍有所布告焉。今人居则曰此阳九之运也。然程子。岂不曰人力可以胜造化乎。十月穷阴。阳尽于上而复生于下。日积一分。至于冬至子半。则宛然一声之雷。万户千门。将次第而开。在人养之之如何耳。故易曰。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凡我同郡之士。其各勉旃。屏绝外慕。无他劳攘。尚论诸老先生而兴起焉。主敬以立其本。讲学以明其善。反躬以践其实。以究石潭体用之全。以合洙泗洛建之传。而鬼魅蹄迹之薮。工商货色之冲。超然无一点之累。则即此一方衣冠。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而玉屏之间。流峙生色。鱼鸟含荣。又非畴昔之比也。呜呼。诸君子盍相与勉之哉。玉屏院仆金乐哲。守护先生墓域甚谨。至是。舍家事。从兰秀。至诚一心供是役。功讫然后乃治私事。亦见秉彝之感而愧死衣裳之族矣。 永历纪元五戊子四月戊申。郡人金平默。记。
足以少慰舆情矣。于是。诸人请平默。记其事之本末。噫。礼义之亡。昔者莘有以为如何。 皇明末叶。罢天下书院。不旋踵其效又如何。然则今日深目高准之祸。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仍有所布告焉。今人居则曰此阳九之运也。然程子。岂不曰人力可以胜造化乎。十月穷阴。阳尽于上而复生于下。日积一分。至于冬至子半。则宛然一声之雷。万户千门。将次第而开。在人养之之如何耳。故易曰。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凡我同郡之士。其各勉旃。屏绝外慕。无他劳攘。尚论诸老先生而兴起焉。主敬以立其本。讲学以明其善。反躬以践其实。以究石潭体用之全。以合洙泗洛建之传。而鬼魅蹄迹之薮。工商货色之冲。超然无一点之累。则即此一方衣冠。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而玉屏之间。流峙生色。鱼鸟含荣。又非畴昔之比也。呜呼。诸君子盍相与勉之哉。玉屏院仆金乐哲。守护先生墓域甚谨。至是。舍家事。从兰秀。至诚一心供是役。功讫然后乃治私事。亦见秉彝之感而愧死衣裳之族矣。 永历纪元五戊子四月戊申。郡人金平默。记。务五斋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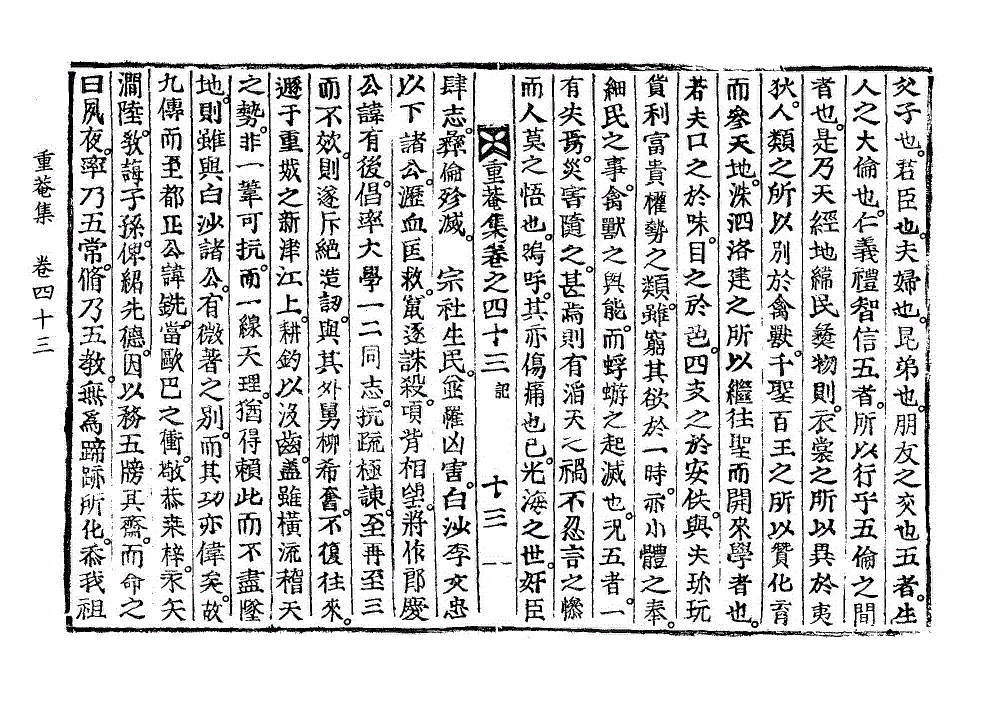 父子也。君臣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生人之大伦也。仁义礼智信五者。所以行乎五伦之间者也。是乃天经地纬民彝物则。衣裳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别于禽兽。千圣百王之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洙泗洛建之所以继往圣而开来学者也。若夫口之于味。目之于色。四支之于安佚。与夫珍玩货利富贵权势之类。虽穷其欲于一时。亦小体之奉。细民之事。禽兽之与能。而蜉蝣之起灭也。况五者。一有失焉。灾害随之。甚焉则有滔天之祸不忍言之惨而人莫之悟也。呜呼。其亦伤痛也已。光海之世。奸臣肆志。彝伦殄灭。 宗社生民。并罹凶害。白沙李文忠以下诸公。沥血匡救。窜逐诛杀。顷背相望。将作郎庆公讳有后。倡率大学一二同志。抗疏极谏。至再至三而不效。则遂斥绝造讱。与其外舅柳希奋。不复往来。遁于重城之新津江上。耕钓以没齿。盖虽横流稽天之势。非一苇可抗。而一线天理。犹得赖此而不尽坠地。则虽与白沙诸公。有微著之别。而其功亦伟矣。故九传而至都正公讳铣。当欧巴之冲。敬恭桑梓。永矢涧陆。教诲子孙。俾绍先德。因以务五榜其斋。而命之曰夙夜。率乃五常。脩乃五教。无为蹄迹所化。忝我祖
父子也。君臣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生人之大伦也。仁义礼智信五者。所以行乎五伦之间者也。是乃天经地纬民彝物则。衣裳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别于禽兽。千圣百王之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洙泗洛建之所以继往圣而开来学者也。若夫口之于味。目之于色。四支之于安佚。与夫珍玩货利富贵权势之类。虽穷其欲于一时。亦小体之奉。细民之事。禽兽之与能。而蜉蝣之起灭也。况五者。一有失焉。灾害随之。甚焉则有滔天之祸不忍言之惨而人莫之悟也。呜呼。其亦伤痛也已。光海之世。奸臣肆志。彝伦殄灭。 宗社生民。并罹凶害。白沙李文忠以下诸公。沥血匡救。窜逐诛杀。顷背相望。将作郎庆公讳有后。倡率大学一二同志。抗疏极谏。至再至三而不效。则遂斥绝造讱。与其外舅柳希奋。不复往来。遁于重城之新津江上。耕钓以没齿。盖虽横流稽天之势。非一苇可抗。而一线天理。犹得赖此而不尽坠地。则虽与白沙诸公。有微著之别。而其功亦伟矣。故九传而至都正公讳铣。当欧巴之冲。敬恭桑梓。永矢涧陆。教诲子孙。俾绍先德。因以务五榜其斋。而命之曰夙夜。率乃五常。脩乃五教。无为蹄迹所化。忝我祖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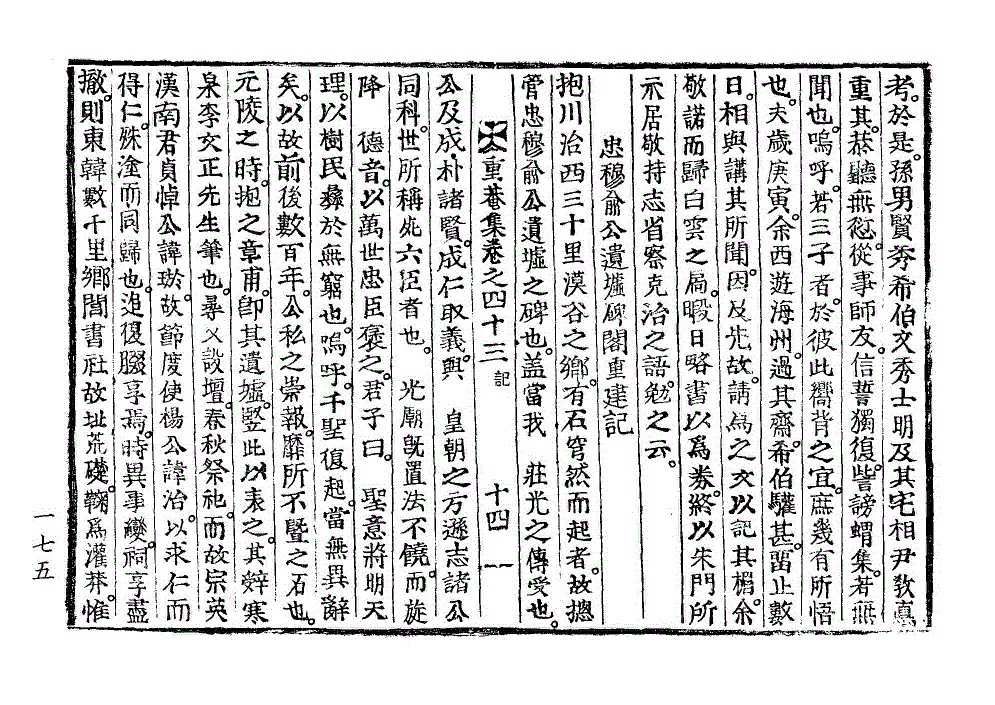 考。于是。孙男贤秀希伯,文秀士明及其宅相尹教德重其。恭听无愆。从事师友。信誓独复。訾谤猬集。若无闻也。呜呼。若三子者。于彼此向背之宜。庶几有所悟也。夫岁庚寅。余西游海州。过其斋。希伯驩甚。留止数日。相与讲其所闻。因及先故。请为之文以记其楣。余敬诺而归白云之扃。暇日略书以为券。终以朱门所示居敬持志省察克治之语。勉之云。
考。于是。孙男贤秀希伯,文秀士明及其宅相尹教德重其。恭听无愆。从事师友。信誓独复。訾谤猬集。若无闻也。呜呼。若三子者。于彼此向背之宜。庶几有所悟也。夫岁庚寅。余西游海州。过其斋。希伯驩甚。留止数日。相与讲其所闻。因及先故。请为之文以记其楣。余敬诺而归白云之扃。暇日略书以为券。终以朱门所示居敬持志省察克治之语。勉之云。忠穆俞公遗墟碑阁重建记
抱川治西三十里漠谷之乡。有石穹然而起者。故总管忠穆俞公遗墟之碑也。盖当我 庄光之传受也。公及成,朴诸贤。成仁取义。与 皇朝之方逊志诸公同科。世所称死六臣者也。 光庙既置法不饶。而旋降 德音。以万世忠臣褒之。君子曰。 圣意将明天理。以树民彝于无穷也。呜呼。千圣复起。当无异辞矣。以故前后数百年。公私之崇报。靡所不暨之石也。元陵之时。抱之章甫。即其遗墟。竖此以表之。其辞寒泉李文正先生笔也。寻乂设坛。春秋祭祀。而故宗英汉南君贞悼公讳𤥽。故节度使杨公讳治。以求仁而得仁。殊涂而同归也。追复啜享焉。时异事变。祠享尽撤。则东韩数千里乡闾书社故址荒础。鞠为灌莽。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6H 页
 有樵儿牧子。啸歌踯躅于其上矣。故流俗所轻士民之无行者。至就漠谷。拔去碑版。葬埋亲尸。而人莫敢谁何则无说矣。公后孙凤在字瑞九。孤寄南服。闻之。出其孤愤。周旋于荐绅章甫之间。掘其入葬。还其碑版。鸠财募工。重建其阁而庇之。访至白云病枕。请为文以记之。平默人微言轻。兼且祸衅馀喘。实不敢攘臂泚笔。然因窃有所感焉。召伯所憩。甘棠不忍拜。孔明所祀。古柏犹可惜。今也则反是。岂好恶之民性。亦有古今之异耶。抑蹄迹之交。风气所驱。有不得不然耶。顾念公当日之祸。忠也。瑞九今日之举。孝也。忠孝之性。即天之经地之义。而向所谓民彝者也。先生尽忠于前。瑞九追孝于后。俯仰可以无愧矣。虽涧藻行潦。俎豆弦诵。追复其旧观。非匹夫之力所能为。自我而可勉者。惟有百尺竿头。进取一步。讲明洙泗洛建。以大忠孝之传。以俟阳复之会而已。瑞九以为如何。永历纪元五庚寅馀分。县人金平默。记。
有樵儿牧子。啸歌踯躅于其上矣。故流俗所轻士民之无行者。至就漠谷。拔去碑版。葬埋亲尸。而人莫敢谁何则无说矣。公后孙凤在字瑞九。孤寄南服。闻之。出其孤愤。周旋于荐绅章甫之间。掘其入葬。还其碑版。鸠财募工。重建其阁而庇之。访至白云病枕。请为文以记之。平默人微言轻。兼且祸衅馀喘。实不敢攘臂泚笔。然因窃有所感焉。召伯所憩。甘棠不忍拜。孔明所祀。古柏犹可惜。今也则反是。岂好恶之民性。亦有古今之异耶。抑蹄迹之交。风气所驱。有不得不然耶。顾念公当日之祸。忠也。瑞九今日之举。孝也。忠孝之性。即天之经地之义。而向所谓民彝者也。先生尽忠于前。瑞九追孝于后。俯仰可以无愧矣。虽涧藻行潦。俎豆弦诵。追复其旧观。非匹夫之力所能为。自我而可勉者。惟有百尺竿头。进取一步。讲明洙泗洛建。以大忠孝之传。以俟阳复之会而已。瑞九以为如何。永历纪元五庚寅馀分。县人金平默。记。二止斋记
崔典籍性佐。起于圃隐先生。倡程朱之学。用夏变夷之邦。年可二十馀。名入桂籍。青云已辟。忽念孔圣富贵浮云之训。孟子东墦酒肉之羞。与夫周子言道充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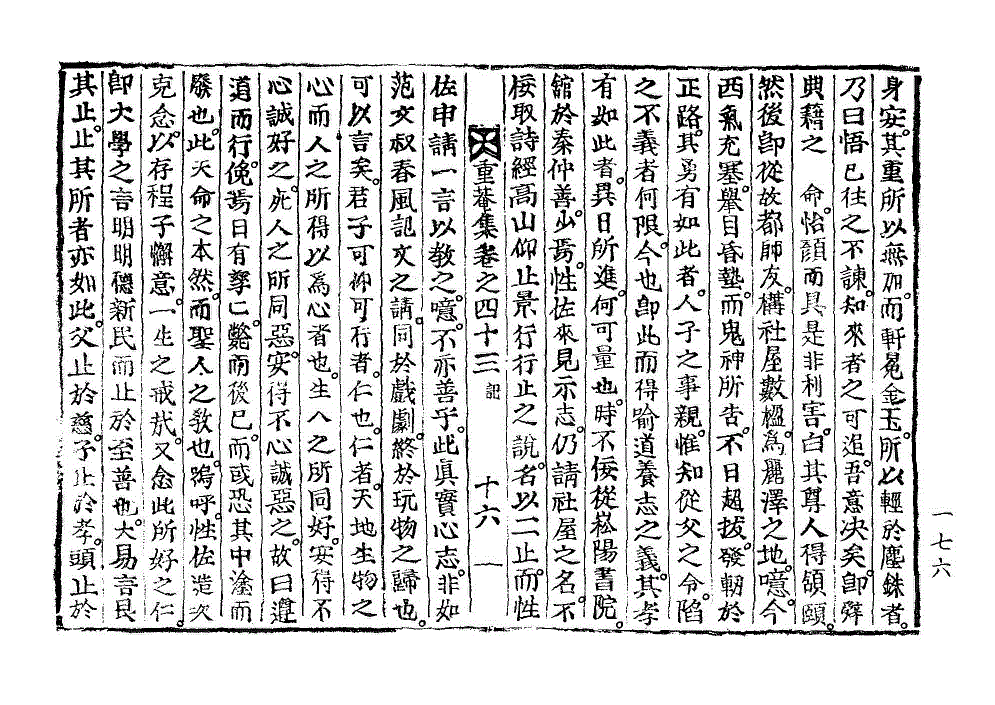 身安。其重所以无加。而轩冕金玉。所以轻于尘铢者。乃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吾意决矣。即辞典籍之 命。怡颜而具是非利害。白其尊人得颔颐。然后即从故都师友。构社屋数楹。为丽泽之地。噫。今西气充塞。举目昏垫。而鬼神所告。不日超拔。发轫于正路。其勇有如此者。人子之事亲。惟知从父之令。陷之不义者何限。今也即此而得喻道养志之义。其孝有如此者。异日所进。何可量也。时不佞从崧阳书院。馆于秦仲善。少焉。性佐来见示志。仍请社屋之名。不佞取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说。名以二止。而性佐申请一言以教之。噫。不亦善乎。此真实心志。非如范文叔春风记文之请。同于戏剧。终于玩物之归也。可以言矣。君子可仰可行者。仁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生人之所同好。安得不心诚好之。死人之所同恶。安得不心诚恶之。故曰遵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而或恐其中涂而废也。此天命之本然。而圣人之教也。呜呼。性佐造次克念。以存程子懈意。一生之戒哉。又念此所好之仁。即大学之言明明德新民而止于至善也。大易言艮其止。止其所者亦如此。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头止于
身安。其重所以无加。而轩冕金玉。所以轻于尘铢者。乃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吾意决矣。即辞典籍之 命。怡颜而具是非利害。白其尊人得颔颐。然后即从故都师友。构社屋数楹。为丽泽之地。噫。今西气充塞。举目昏垫。而鬼神所告。不日超拔。发轫于正路。其勇有如此者。人子之事亲。惟知从父之令。陷之不义者何限。今也即此而得喻道养志之义。其孝有如此者。异日所进。何可量也。时不佞从崧阳书院。馆于秦仲善。少焉。性佐来见示志。仍请社屋之名。不佞取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说。名以二止。而性佐申请一言以教之。噫。不亦善乎。此真实心志。非如范文叔春风记文之请。同于戏剧。终于玩物之归也。可以言矣。君子可仰可行者。仁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生人之所同好。安得不心诚好之。死人之所同恶。安得不心诚恶之。故曰遵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而或恐其中涂而废也。此天命之本然。而圣人之教也。呜呼。性佐造次克念。以存程子懈意。一生之戒哉。又念此所好之仁。即大学之言明明德新民而止于至善也。大易言艮其止。止其所者亦如此。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头止于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7H 页
 直。目止于端。貌止于恭。言止于忠。凡天地之间日用动静。若大若小。皆止于至善之说。觚不觚觚哉觚哉。呜呼。性佐因是而熟讲于师友。以至于心通其妙哉。呜呼。吾坐在昏垫。寤寐反侧。窃愿为三圣之徒者也。以此久锢不齿。朝夕就木。不得少须臾及见。然至是亦将游魂于松岳天马之间。驩忻慰悦之不已也。 永历五庚寅应钟节。清风金平默。记。
直。目止于端。貌止于恭。言止于忠。凡天地之间日用动静。若大若小。皆止于至善之说。觚不觚觚哉觚哉。呜呼。性佐因是而熟讲于师友。以至于心通其妙哉。呜呼。吾坐在昏垫。寤寐反侧。窃愿为三圣之徒者也。以此久锢不齿。朝夕就木。不得少须臾及见。然至是亦将游魂于松岳天马之间。驩忻慰悦之不已也。 永历五庚寅应钟节。清风金平默。记。谨宁君祠堂记
我 恭定王别子谨宁君。性行躬躬。守正不挠。当 光庙时。不署靖难勋。临终治命。无得受礼葬。大致与三相六臣同归。世言 庄陵忠臣数六。宗英。公其一也。 中庙戊寅。从静庵赵文正 筵白。依礼 命不祧。并 赐守庙人十户。牲杀亦岁供。庙在全义治南松谷之里。久而颓圮。宗孙斗相。与族人承旭元相等。集议鸠财。始于今 上己丑。越明年。工告迄功。栋宇丹雘。一复其旧。识者。谓天下之理。感与应而已。公以河间东平之姿。天经民彝。向背不差。盖不知方逊志诸公为何如。则百世不迁。虽先王制礼之常。而其所以受报酬功。称思于永久。非专以别子之例典也。 光庙于三相六臣。置法不贳矣。旋又曰。当代之乱臣。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7L 页
 万世之忠臣。 圣意盖将明天理树彝教于无穷。则贵戚异姓。其抑扬何以异哉。因是而有感焉。我东胜国之时。殷师世远。贸贸而夷也。 康献大王。以盛德至善。宜家以教国。自是 圣圣相承。惟道是揆。礼义之风振天下。即公子王孙。茶饭擩染。可知也。以故得维持巩固五百年。而无一日土崩之祸。呜呼。此宁可以不知耶。凡为公之后昆者。深惟此理之不忒。祇事宗子。睦及全族。敬恭蚤夜。相与力学。门成邹鲁。户为洛建。仰答 祖宗之意。不但春秋祭祀蘋藻馨香而已。则欧罗腥膻。无分毫之杂。而子孙千亿。将见如日之升如松之茂而如南山之寿矣。承旭少学于任鼓山宪晦。宋祭酒秉璿。今菀有名实。元相耻爵禄之縻不以其道。尘视而不取。其耿介如此。非汩没人也。吾且跂足而俟之也。 永历纪元五庚寅阳复初吉。清城金平默。记。
万世之忠臣。 圣意盖将明天理树彝教于无穷。则贵戚异姓。其抑扬何以异哉。因是而有感焉。我东胜国之时。殷师世远。贸贸而夷也。 康献大王。以盛德至善。宜家以教国。自是 圣圣相承。惟道是揆。礼义之风振天下。即公子王孙。茶饭擩染。可知也。以故得维持巩固五百年。而无一日土崩之祸。呜呼。此宁可以不知耶。凡为公之后昆者。深惟此理之不忒。祇事宗子。睦及全族。敬恭蚤夜。相与力学。门成邹鲁。户为洛建。仰答 祖宗之意。不但春秋祭祀蘋藻馨香而已。则欧罗腥膻。无分毫之杂。而子孙千亿。将见如日之升如松之茂而如南山之寿矣。承旭少学于任鼓山宪晦。宋祭酒秉璿。今菀有名实。元相耻爵禄之縻不以其道。尘视而不取。其耿介如此。非汩没人也。吾且跂足而俟之也。 永历纪元五庚寅阳复初吉。清城金平默。记。北青二孝子旌闾记
上之庚寅。咸镜道前进士李河信等上言。北青故学生李时聃及其弟圣聃。青海伯襄烈公之兰之十三世孙也。世笃忠孝。其父为人所诬。不得其死。时聃兄弟抱尸号哭。便即执其仇。手刃以报之。诣官请死。系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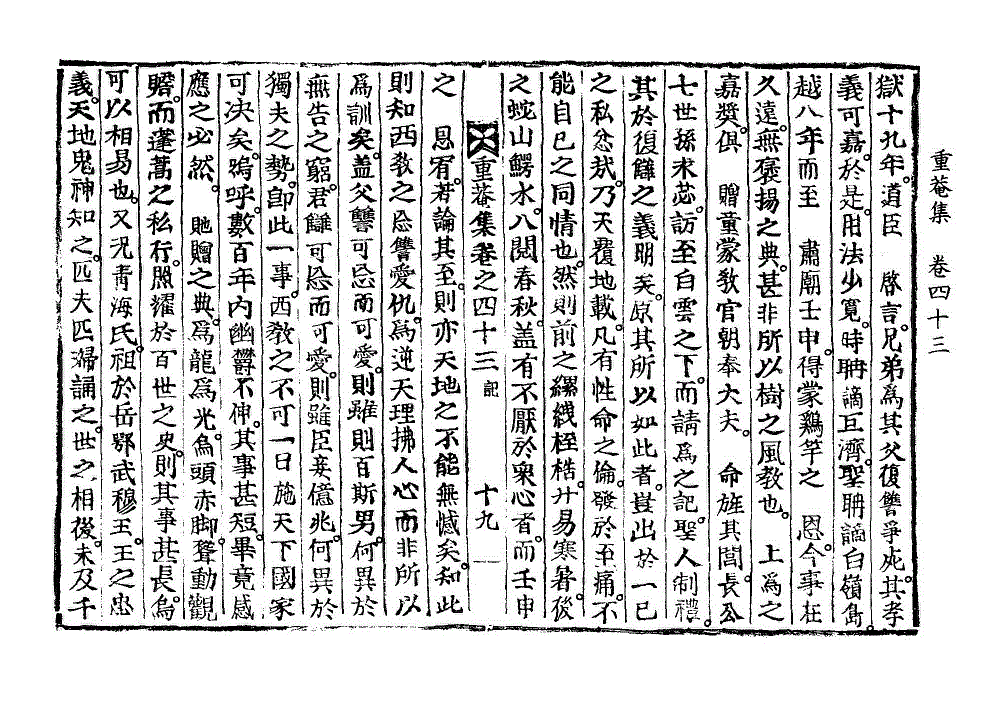 狱十九年。道臣 启言。兄弟为其父复雠争死。其孝义可嘉。于是。用法少宽。时聃谪巨济。圣聃谪白岭岛。越八年而至 肃庙壬申。得蒙鸡竿之 恩。今事在久远。无褒扬之典。甚非所以树之风教也。 上为之嘉奖。俱 赠童蒙教官朝奉大夫。 命旌其闾。长公七世孙求苾。访至白云之下。而请为之记。圣人制礼。其于复雠之义明矣。原其所以如此者。岂出于一己之私忿哉。乃天覆地载。凡有性命之伦。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也。然则前之缧绁桎梏。廿易寒暑。后之蛇山鳄水。八阅春秋。盖有不厌于众心者。而壬申之 恩宥。若论其至。则亦天地之不能无憾矣。知此则知西教之忘雠爱仇。为逆天理拂人心而非所以为训矣。盖父雠可忘而可爱。则虽则百斯男。何异于无告之穷。君雠可忘而可爱。则虽臣妾亿兆。何异于独夫之势。即此一事。西教之不可一日施天下国家可决矣。呜呼。数百年内幽郁不伸。其事甚短。毕竟感应之必然。 貤赠之典。为龙为光。乌头赤脚。耸动观瞻。而蓬蒿之私行。照耀于百世之史。则其事甚长。乌可以相易也。又况青海氏。祖于岳鄂武穆王。王之忠义。天地鬼神知之。匹夫匹妇诵之。世之相后。未及千
狱十九年。道臣 启言。兄弟为其父复雠争死。其孝义可嘉。于是。用法少宽。时聃谪巨济。圣聃谪白岭岛。越八年而至 肃庙壬申。得蒙鸡竿之 恩。今事在久远。无褒扬之典。甚非所以树之风教也。 上为之嘉奖。俱 赠童蒙教官朝奉大夫。 命旌其闾。长公七世孙求苾。访至白云之下。而请为之记。圣人制礼。其于复雠之义明矣。原其所以如此者。岂出于一己之私忿哉。乃天覆地载。凡有性命之伦。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也。然则前之缧绁桎梏。廿易寒暑。后之蛇山鳄水。八阅春秋。盖有不厌于众心者。而壬申之 恩宥。若论其至。则亦天地之不能无憾矣。知此则知西教之忘雠爱仇。为逆天理拂人心而非所以为训矣。盖父雠可忘而可爱。则虽则百斯男。何异于无告之穷。君雠可忘而可爱。则虽臣妾亿兆。何异于独夫之势。即此一事。西教之不可一日施天下国家可决矣。呜呼。数百年内幽郁不伸。其事甚短。毕竟感应之必然。 貤赠之典。为龙为光。乌头赤脚。耸动观瞻。而蓬蒿之私行。照耀于百世之史。则其事甚长。乌可以相易也。又况青海氏。祖于岳鄂武穆王。王之忠义。天地鬼神知之。匹夫匹妇诵之。世之相后。未及千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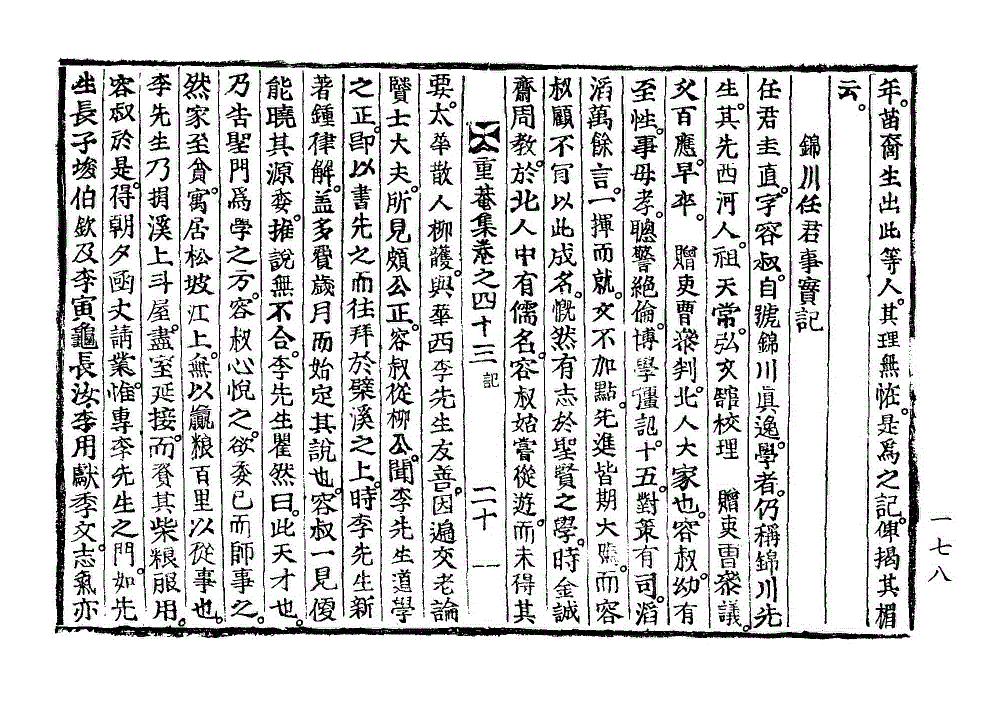 年。苗裔生出此等人。其理无怪。是为之记。俾揭其楣云。
年。苗裔生出此等人。其理无怪。是为之记。俾揭其楣云。锦川任君事实记
任君圭直。字容叔。自号锦川真逸。学者。仍称锦川先生。其先西河人。祖天常。弘文馆校理 赠吏曹参议。父百应。早卒。 赠吏曹参判。北人大家也。容叔。幼有至性。事母孝。聪警绝伦。博学彊记。十五。对策有司。滔滔万馀言。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先进皆期大鸣。而容叔顾不肯以此成名。慨然有志于圣贤之学。时金诚斋周教。于北人中有儒名。容叔始尝从游。而未得其要。太华散人柳頀。与华西李先生友善。因遍交老论贤士大夫。所见颇公正。容叔从柳公。闻李先生道学之正。即以书先之而往拜于檗溪之上。时李先生新著钟律解。盖多费岁月而始定其说也。容叔一见便能晓其源委。推说无不合。李先生瞿然曰。此天才也。乃告圣门为学之方。容叔心悦之。欲委己而师事之。然家至贫。寓居松坡江上。无以赢粮百里以从事也。李先生乃捐溪上斗屋。尽室延接。而资其柴粮服用。容叔于是。得朝夕函丈请业。惟专李先生之门。如先生长子埈伯钦及李寅龟长汝,李用献季文。志气亦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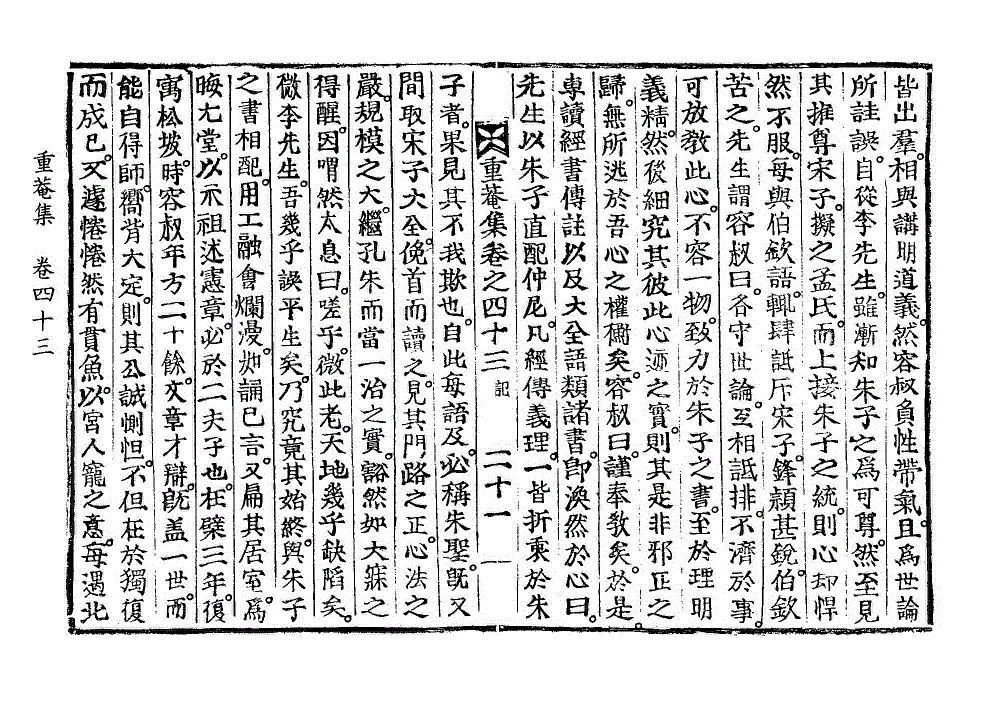 皆出群。相与讲明道义。然容叔负性带气。且为世论所诖误。自从李先生。虽渐知朱子之为可尊。然至见其推尊宋子。拟之孟氏。而上接朱子之统。则心却悍然不服。每与伯钦语。辄肆诋斥宋子。锋颖甚锐。伯钦苦之。先生谓容叔曰。各守世论。互相诋排。不济于事。可放教此心。不容一物。致力于朱子之书。至于理明义精。然后细究其彼此心迹之实。则其是非邪正之归。无所逃于吾心之权衡矣。容叔曰。谨奉教矣。于是。专读经书传注以及大全语类诸书。即涣然于心曰。先生以朱子直配仲尼。凡经传义理。一皆折衷于朱子者。果见其不我欺也。自此每语及。必称朱圣。既又间取宋子大全。俛首而读之。见其门路之正。心法之严。规模之大。继孔朱而当一治之实。豁然如大寐之得醒。因喟然太息曰。嗟乎。微此老。天地几乎缺陷矣。微李先生。吾几乎误平生矣。乃究竟其始终。与朱子之书相配。用工融会烂漫。如诵己言。又扁其居室。为晦尤堂。以示祖述宪章。必于二夫子也。在檗三年。复寓松坡。时容叔年方二十馀。文章才辩。既盖一世。而能自得师。向背大定。则其公诚恻怛。不但在于独复而成己。又遽惓惓然有贯鱼。以宫人宠之意。每遇北
皆出群。相与讲明道义。然容叔负性带气。且为世论所诖误。自从李先生。虽渐知朱子之为可尊。然至见其推尊宋子。拟之孟氏。而上接朱子之统。则心却悍然不服。每与伯钦语。辄肆诋斥宋子。锋颖甚锐。伯钦苦之。先生谓容叔曰。各守世论。互相诋排。不济于事。可放教此心。不容一物。致力于朱子之书。至于理明义精。然后细究其彼此心迹之实。则其是非邪正之归。无所逃于吾心之权衡矣。容叔曰。谨奉教矣。于是。专读经书传注以及大全语类诸书。即涣然于心曰。先生以朱子直配仲尼。凡经传义理。一皆折衷于朱子者。果见其不我欺也。自此每语及。必称朱圣。既又间取宋子大全。俛首而读之。见其门路之正。心法之严。规模之大。继孔朱而当一治之实。豁然如大寐之得醒。因喟然太息曰。嗟乎。微此老。天地几乎缺陷矣。微李先生。吾几乎误平生矣。乃究竟其始终。与朱子之书相配。用工融会烂漫。如诵己言。又扁其居室。为晦尤堂。以示祖述宪章。必于二夫子也。在檗三年。复寓松坡。时容叔年方二十馀。文章才辩。既盖一世。而能自得师。向背大定。则其公诚恻怛。不但在于独复而成己。又遽惓惓然有贯鱼。以宫人宠之意。每遇北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79L 页
 人。必极言竭论。悉敷肾肠而不自止。其于南人,少论亦然。其言曰朱子圣人也。宋子大贤也。学者当以朱圣为主。欲学朱圣。当以宋子为法。道之在天下。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至出入起居食息语默。皆有一定之理。不可有毫发之移。易顷刻之废弛也。故自古圣贤垂教天下后世者。不遗馀力。然孟子没。道学失传。士之所求于圣贤之书。不越乎记诵文辞之间。而异端之说日炽。学者无所据而入也。幸周程诸子。始续千载不传之绪。至朱子则既尽得周程所传。而明诚之极。至于能化。既不异于圣人矣。于是。竭其精力。各就圣贤之书。解释其本义。凡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莫不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所遗。使尧舜以来相传之道。豁然如大明中天。有目者可睹焉。其继往开来之功。无愧于前圣矣。其他嘉言懿旨。具载于大全语类者。无不亲切精当。的确浑圆。盖无一理之不明。一事之或遗也。欲学圣贤。不以朱圣为主而奚可哉。然朱圣之后。中国之学。专尚陆,王。其效至于戎虏八主。四海腥膻。而道之托于人者绝矣。何幸我东静,退,栗,牛诸贤辈出。皆能钦崇服习而至于宋子。则致知存养。
人。必极言竭论。悉敷肾肠而不自止。其于南人,少论亦然。其言曰朱子圣人也。宋子大贤也。学者当以朱圣为主。欲学朱圣。当以宋子为法。道之在天下。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至出入起居食息语默。皆有一定之理。不可有毫发之移。易顷刻之废弛也。故自古圣贤垂教天下后世者。不遗馀力。然孟子没。道学失传。士之所求于圣贤之书。不越乎记诵文辞之间。而异端之说日炽。学者无所据而入也。幸周程诸子。始续千载不传之绪。至朱子则既尽得周程所传。而明诚之极。至于能化。既不异于圣人矣。于是。竭其精力。各就圣贤之书。解释其本义。凡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莫不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所遗。使尧舜以来相传之道。豁然如大明中天。有目者可睹焉。其继往开来之功。无愧于前圣矣。其他嘉言懿旨。具载于大全语类者。无不亲切精当。的确浑圆。盖无一理之不明。一事之或遗也。欲学圣贤。不以朱圣为主而奚可哉。然朱圣之后。中国之学。专尚陆,王。其效至于戎虏八主。四海腥膻。而道之托于人者绝矣。何幸我东静,退,栗,牛诸贤辈出。皆能钦崇服习而至于宋子。则致知存养。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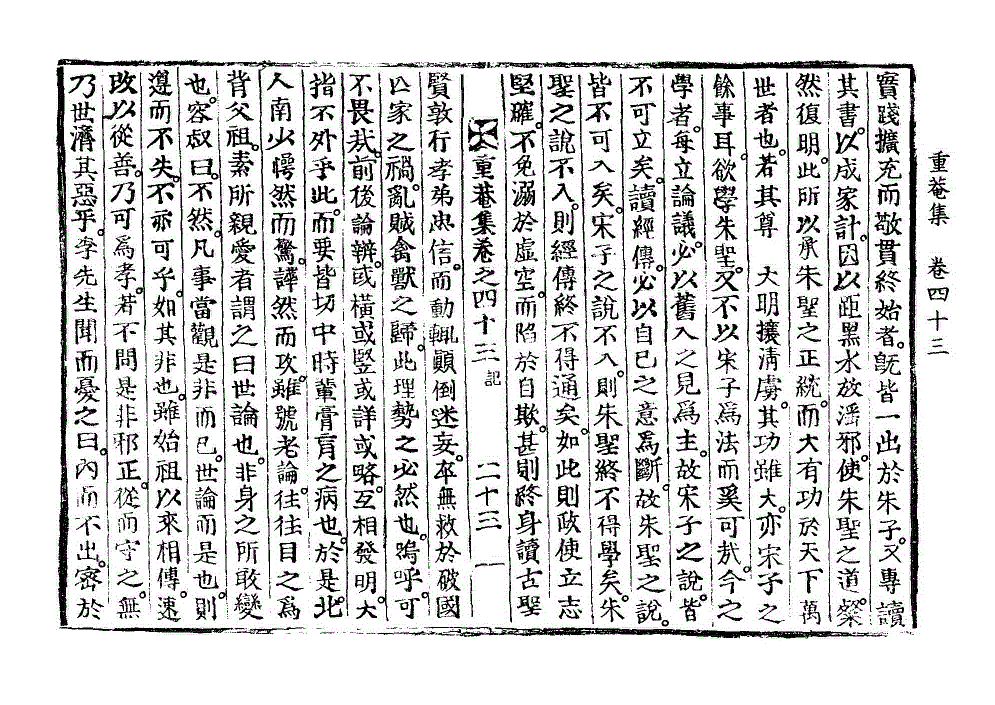 实践扩充而敬贯终始者。既皆一出于朱子。又专读其书。以成家计。因以距黑水放淫邪。使朱圣之道。粲然复明。此所以承朱圣之正统。而大有功于天下万世者也。若其尊 大明攘清虏。其功虽大。亦宋子之馀事耳。欲学朱圣。又不以宋子为法而奚可哉。今之学者。每立论议。必以旧入之见为主。故宋子之说。皆不可立矣。读经传。必以自己之意为断。故朱圣之说。皆不可入矣。宋子之说不入。则朱圣终不得学矣。朱圣之说不入。则经传终不得通矣。如此则政使立志坚确。不免溺于虚空。而陷于自欺。甚则终身读古圣贤敦行孝弟忠信。而动辄颠倒迷妄。卒无救于破国亡家之祸。乱贼禽兽之归。此理势之必然也。呜呼。可不畏哉。前后论辨。或横或竖或详或略。互相发明。大指不外乎此。而要皆切中时辈膏肓之病也。于是。北人南少愕然而惊。哗然而攻。虽号老论。往往目之为背父祖。素所亲爱者谓之曰世论也。非身之所敢变也。容叔曰。不然。凡事当观是非而已。世论而是也。则遵而不失。不亦可乎。如其非也。虽始祖以来相传。速改以从善。乃可为孝。若不问是非邪正。从而守之。无乃世济其恶乎。李先生闻而忧之曰。内而不出。密于
实践扩充而敬贯终始者。既皆一出于朱子。又专读其书。以成家计。因以距黑水放淫邪。使朱圣之道。粲然复明。此所以承朱圣之正统。而大有功于天下万世者也。若其尊 大明攘清虏。其功虽大。亦宋子之馀事耳。欲学朱圣。又不以宋子为法而奚可哉。今之学者。每立论议。必以旧入之见为主。故宋子之说。皆不可立矣。读经传。必以自己之意为断。故朱圣之说。皆不可入矣。宋子之说不入。则朱圣终不得学矣。朱圣之说不入。则经传终不得通矣。如此则政使立志坚确。不免溺于虚空。而陷于自欺。甚则终身读古圣贤敦行孝弟忠信。而动辄颠倒迷妄。卒无救于破国亡家之祸。乱贼禽兽之归。此理势之必然也。呜呼。可不畏哉。前后论辨。或横或竖或详或略。互相发明。大指不外乎此。而要皆切中时辈膏肓之病也。于是。北人南少愕然而惊。哗然而攻。虽号老论。往往目之为背父祖。素所亲爱者谓之曰世论也。非身之所敢变也。容叔曰。不然。凡事当观是非而已。世论而是也。则遵而不失。不亦可乎。如其非也。虽始祖以来相传。速改以从善。乃可为孝。若不问是非邪正。从而守之。无乃世济其恶乎。李先生闻而忧之曰。内而不出。密于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0L 页
 自治。可也。今乃危言而不讱。是犹孤军单骑。无蚍蜉蚁子之援。而犯貔貅百万之锋也。乃贻书深戒之。容叔不能从。容叔尝对彼类。洞辨尹鑴之罪。李先生戏谓容叔曰。死鑴。子固如此。若遇生鑴。如之何。对曰。圭直以死者。故如是而已。于生者则岂肯止此。且圭直之严于死者。所以深恶夫生者也。因曰。距邪辟淫。如春秋之法。不必圣贤人人得以攻之。则固不敢回互媕婀。有志于学者。为邪说所迷误。又不忍不救。虽以此得罪而死。万无恨矣。于是。时辈目为新老论。谤讟益如河漫海溢。容叔贻书于人曰。此汉得好题目矣。虽人斫我头去。尤翁不可不学。彼鼓发狂闹。何足以动吾一发。又曰。愚之尊尤翁。岂有他哉。以斯文在玆也。南少中苟有如尤翁者。愚岂不以尊尤翁者尊之也。然则又将以南人少论目我乎。自有朋党以来。人各世守其论。不求其邪正是非之所在。所谓老论者。亦以尤翁为偏党之长。而不知其所以为尤翁者。故于阴阳黑白。懵然不辨。胥溺于邪诐。况他人之唤阳作阴。指白为黑。而打成一片者乎。试看今日老论。尊信尤翁有如此汉者乎。今日老论之所不足信者。愚以北人。乃尊信如是。则是必有所以矣。此岂非所谓
自治。可也。今乃危言而不讱。是犹孤军单骑。无蚍蜉蚁子之援。而犯貔貅百万之锋也。乃贻书深戒之。容叔不能从。容叔尝对彼类。洞辨尹鑴之罪。李先生戏谓容叔曰。死鑴。子固如此。若遇生鑴。如之何。对曰。圭直以死者。故如是而已。于生者则岂肯止此。且圭直之严于死者。所以深恶夫生者也。因曰。距邪辟淫。如春秋之法。不必圣贤人人得以攻之。则固不敢回互媕婀。有志于学者。为邪说所迷误。又不忍不救。虽以此得罪而死。万无恨矣。于是。时辈目为新老论。谤讟益如河漫海溢。容叔贻书于人曰。此汉得好题目矣。虽人斫我头去。尤翁不可不学。彼鼓发狂闹。何足以动吾一发。又曰。愚之尊尤翁。岂有他哉。以斯文在玆也。南少中苟有如尤翁者。愚岂不以尊尤翁者尊之也。然则又将以南人少论目我乎。自有朋党以来。人各世守其论。不求其邪正是非之所在。所谓老论者。亦以尤翁为偏党之长。而不知其所以为尤翁者。故于阴阳黑白。懵然不辨。胥溺于邪诐。况他人之唤阳作阴。指白为黑。而打成一片者乎。试看今日老论。尊信尤翁有如此汉者乎。今日老论之所不足信者。愚以北人。乃尊信如是。则是必有所以矣。此岂非所谓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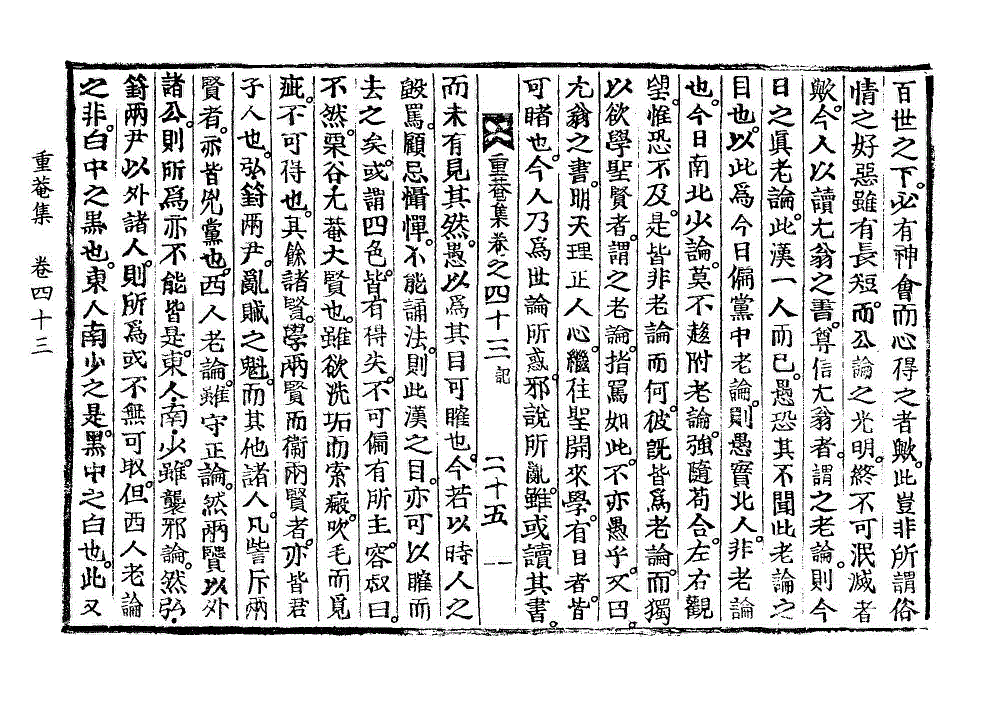 百世之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欤。此岂非所谓俗情之好恶虽有长短。而公论之光明。终不可泯灭者欤。今人以读尤翁之书。尊信尤翁者。谓之老论。则今日之真老论。此汉一人而已。愚恐其不闻此老论之目也。以此为今日偏党中老论。则愚实北人。非老论也。今日南北少论。莫不趍附老论。强随苟合。左右观望。惟恐不及。是皆非老论而何。彼既皆为老论。而独以欲学圣贤者。谓之老论。指骂如此。不亦愚乎。又曰。尤翁之书。明天理正人心。继往圣开来学。有目者。皆可睹也。今人乃为世论所惑。邪说所乱。虽或读其书。而未有见其然。愚以为其目可𥉑也。今若以时人之毁骂。顾忌慑惮。不能诵法。则此汉之目。亦可以𥉑而去之矣。或谓四色。皆有得失。不可偏有所主。容叔曰。不然。栗谷,尤庵大贤也。虽欲洗垢而索瘢。吹毛而觅疵。不可得也。其馀诸贤。学两贤而卫两贤者。亦皆君子人也。弘,篈两尹。乱贼之魁。而其他诸人。凡訾斥两贤者。亦皆凶党也。西人老论。虽守正论。然两贤以外诸公。则所为亦不能皆是。东人,南,少。虽袭邪论。然弘,篈两尹以外诸人。则所为或不无可取。但西人老论之非。白中之黑也。东人南少之是。黑中之白也。此又
百世之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欤。此岂非所谓俗情之好恶虽有长短。而公论之光明。终不可泯灭者欤。今人以读尤翁之书。尊信尤翁者。谓之老论。则今日之真老论。此汉一人而已。愚恐其不闻此老论之目也。以此为今日偏党中老论。则愚实北人。非老论也。今日南北少论。莫不趍附老论。强随苟合。左右观望。惟恐不及。是皆非老论而何。彼既皆为老论。而独以欲学圣贤者。谓之老论。指骂如此。不亦愚乎。又曰。尤翁之书。明天理正人心。继往圣开来学。有目者。皆可睹也。今人乃为世论所惑。邪说所乱。虽或读其书。而未有见其然。愚以为其目可𥉑也。今若以时人之毁骂。顾忌慑惮。不能诵法。则此汉之目。亦可以𥉑而去之矣。或谓四色。皆有得失。不可偏有所主。容叔曰。不然。栗谷,尤庵大贤也。虽欲洗垢而索瘢。吹毛而觅疵。不可得也。其馀诸贤。学两贤而卫两贤者。亦皆君子人也。弘,篈两尹。乱贼之魁。而其他诸人。凡訾斥两贤者。亦皆凶党也。西人老论。虽守正论。然两贤以外诸公。则所为亦不能皆是。东人,南,少。虽袭邪论。然弘,篈两尹以外诸人。则所为或不无可取。但西人老论之非。白中之黑也。东人南少之是。黑中之白也。此又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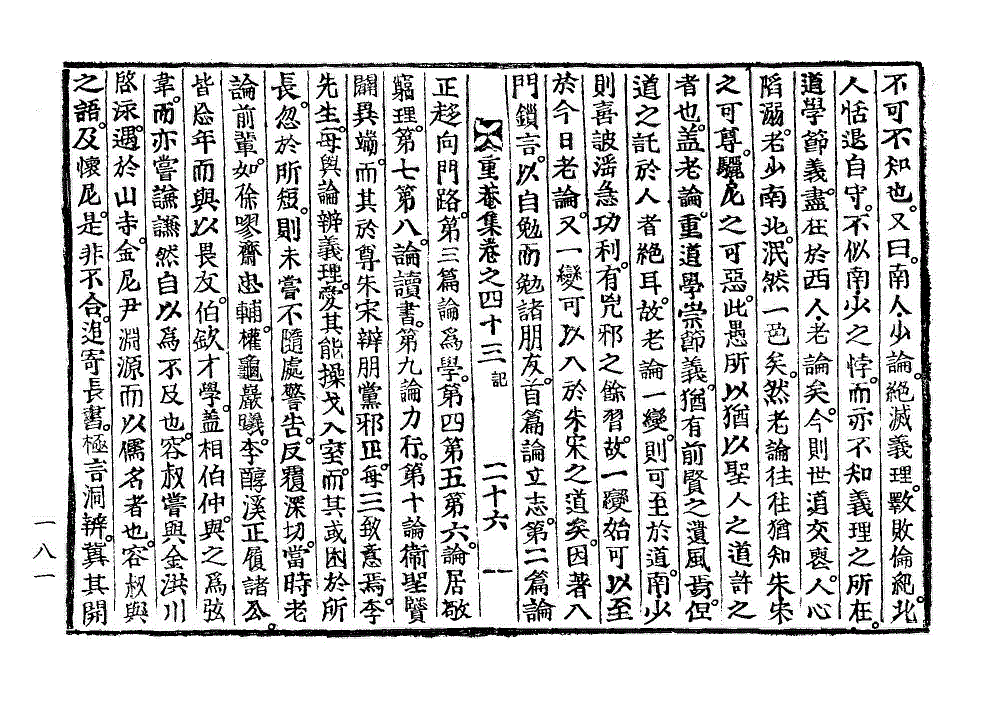 不可不知也。又曰。南人,少论。绝灭义理。斁败伦纪。北人恬退自守。不似南,少之悖。而亦不知义理之所在。道学节义。尽在于西人,老论矣。今则世道交丧。人心陷溺。老少南北。泯然一色矣。然老论往往犹知朱,宋之可尊。骊,尼之可恶。此愚所以犹以圣人之道许之者也。盖老论。重道学崇节义。犹有前贤之遗风焉。但道之托于人者绝耳。故老论一变。则可至于道。南,少则喜诐淫急功利。有凶邪之馀习。故一变始可以至于今日老论。又一变可以入于朱,宋之道矣。因著入门锁言。以自勉而勉诸朋友。首篇论立志。第二篇论正趍向门路。第三篇论为学。第四第五第六。论居敬穷理。第七第八。论读书。第九论力行。第十论卫圣贤辟异端。而其于尊朱宋辨朋党邪正。每三致意焉。李先生。每与论辨义理。爱其能操戈入室。而其或困于所长。忽于所短。则未尝不随处警告。反覆深切。当时老论前辈。如徐嘐斋忠辅。权龟岩曦。李醇溪正履诸公。皆忘年而与以畏友。伯钦才学。盖相伯仲。与之为弦韦。而亦尝谦谦然自以为不及也。容叔尝与金洪川启泳。遇于山寺。金尼尹渊源而以儒名者也。容叔与之语。及怀尼。是非不合。追寄长书。极言洞辨。冀其开
不可不知也。又曰。南人,少论。绝灭义理。斁败伦纪。北人恬退自守。不似南,少之悖。而亦不知义理之所在。道学节义。尽在于西人,老论矣。今则世道交丧。人心陷溺。老少南北。泯然一色矣。然老论往往犹知朱,宋之可尊。骊,尼之可恶。此愚所以犹以圣人之道许之者也。盖老论。重道学崇节义。犹有前贤之遗风焉。但道之托于人者绝耳。故老论一变。则可至于道。南,少则喜诐淫急功利。有凶邪之馀习。故一变始可以至于今日老论。又一变可以入于朱,宋之道矣。因著入门锁言。以自勉而勉诸朋友。首篇论立志。第二篇论正趍向门路。第三篇论为学。第四第五第六。论居敬穷理。第七第八。论读书。第九论力行。第十论卫圣贤辟异端。而其于尊朱宋辨朋党邪正。每三致意焉。李先生。每与论辨义理。爱其能操戈入室。而其或困于所长。忽于所短。则未尝不随处警告。反覆深切。当时老论前辈。如徐嘐斋忠辅。权龟岩曦。李醇溪正履诸公。皆忘年而与以畏友。伯钦才学。盖相伯仲。与之为弦韦。而亦尝谦谦然自以为不及也。容叔尝与金洪川启泳。遇于山寺。金尼尹渊源而以儒名者也。容叔与之语。及怀尼。是非不合。追寄长书。极言洞辨。冀其开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2H 页
 悟于万一也。金得书大怒。以示朴相宗薰。朴相深衔之。伯钦亦以称美容叔。故积忤于乡党少论。而齽齘之口至及于先生也。既而膺中狱起。辞连容叔。时 宪庙丙申也。膺中与容叔。素有姻诐而未曾相识。会膺中之兄迥中。来见容叔。颇示愿学之意。力劝其挈家而南。团聚讲业。仍馈之金。使为行赀。此时逆节已萌。而容叔不之知也。特于辞气之间。见其非吉人。巽辞而不许。迥中辞以周穷。弃金而去。猝无使唤可追还。姑且坚封而深藏之。将求顺便而还之。容叔竟以是被逮。举实以供。且纳封金。狱中日诵大学,朱宋书。阳阳如平常。丁酉膺迥伏诛。大臣洪公奭周。捕将金公镆。察其冤状而力伸之。容叔于是当白放。朴相争之曰。彼持身不谨。交结逆竖。恶得无罪。遂定配金堤郡。当容叔之持正论也。北人虽嫉之如仇敌。而其中天质粹美。持心公平者。为至诚所动。亦能八九分开悟。若无是祸而持之以岁月。则犹可以救拔多少人物。不但寥寥而已也。容叔既窜。贤士大夫。莫不冤之。梅山洪文敬公直弼。栗里柳公荣五。青墅任公翼常。李进士审爟。及李醇溪诸公。迭相讼冤于当路。赵相国寅永。 国舅丰恩府院君万永。皆欣然听之。癸卯
悟于万一也。金得书大怒。以示朴相宗薰。朴相深衔之。伯钦亦以称美容叔。故积忤于乡党少论。而齽齘之口至及于先生也。既而膺中狱起。辞连容叔。时 宪庙丙申也。膺中与容叔。素有姻诐而未曾相识。会膺中之兄迥中。来见容叔。颇示愿学之意。力劝其挈家而南。团聚讲业。仍馈之金。使为行赀。此时逆节已萌。而容叔不之知也。特于辞气之间。见其非吉人。巽辞而不许。迥中辞以周穷。弃金而去。猝无使唤可追还。姑且坚封而深藏之。将求顺便而还之。容叔竟以是被逮。举实以供。且纳封金。狱中日诵大学,朱宋书。阳阳如平常。丁酉膺迥伏诛。大臣洪公奭周。捕将金公镆。察其冤状而力伸之。容叔于是当白放。朴相争之曰。彼持身不谨。交结逆竖。恶得无罪。遂定配金堤郡。当容叔之持正论也。北人虽嫉之如仇敌。而其中天质粹美。持心公平者。为至诚所动。亦能八九分开悟。若无是祸而持之以岁月。则犹可以救拔多少人物。不但寥寥而已也。容叔既窜。贤士大夫。莫不冤之。梅山洪文敬公直弼。栗里柳公荣五。青墅任公翼常。李进士审爟。及李醇溪诸公。迭相讼冤于当路。赵相国寅永。 国舅丰恩府院君万永。皆欣然听之。癸卯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2L 页
 得蒙 宥。梅山先生贻书伯钦曰。为我道任君。自今销声屏气。寂寂若地下人也。时朴相之子醇寿。坐逆狱诛死。人谓神明报应。其功如此。容叔在金堤。洪先生见郡守赵公秉宪及赵公弟肃斋秉德。诵其贤而辨其冤状甚悉。赵公兄弟。遂造其谪庐而礼貌之。肃斋尝师事洪先生。以经行闻于湖中。见容叔。恨相知之晚也。遣其子弟从学。四方学者闻而归之者亦众。至是容叔。无意居京辇近地。赵公为设馆于其恩津乡第。容叔既宥。东入檗溪而见先生。先生与其流放困㞃志气不挫。因以充养本源。克勤小物申勉之。且曰。洪公与子。无倾盖之旧。而嘉子之归正。保子之无罪。累言于廊庙诸公。使子卒蒙 大恩。归侍慈颜。朋友讲习。此古所谓知己也。容叔曰。叔向不见祁奚。范滂不谢霍谞。但此丈德行。为世达尊。敢不往见。遂一再至鹭江。拜谢请教。仍质大学明德之说。已而自恩津。迁蓝浦。丁母夫人忧。哀毁过节。忧吉。转徙尚州以卒。时 哲宗癸丑也。距其生。 纯祖辛未。年四十三。朝廷始授缮工监役。闻其殁不施。季文,伯钦。时亦早殁。长汝年六十馀。穷居丹阳之山。李先生 哲考壬戌。名出贼招。被缧绁。今 上元年。第七十馀。始授台
得蒙 宥。梅山先生贻书伯钦曰。为我道任君。自今销声屏气。寂寂若地下人也。时朴相之子醇寿。坐逆狱诛死。人谓神明报应。其功如此。容叔在金堤。洪先生见郡守赵公秉宪及赵公弟肃斋秉德。诵其贤而辨其冤状甚悉。赵公兄弟。遂造其谪庐而礼貌之。肃斋尝师事洪先生。以经行闻于湖中。见容叔。恨相知之晚也。遣其子弟从学。四方学者闻而归之者亦众。至是容叔。无意居京辇近地。赵公为设馆于其恩津乡第。容叔既宥。东入檗溪而见先生。先生与其流放困㞃志气不挫。因以充养本源。克勤小物申勉之。且曰。洪公与子。无倾盖之旧。而嘉子之归正。保子之无罪。累言于廊庙诸公。使子卒蒙 大恩。归侍慈颜。朋友讲习。此古所谓知己也。容叔曰。叔向不见祁奚。范滂不谢霍谞。但此丈德行。为世达尊。敢不往见。遂一再至鹭江。拜谢请教。仍质大学明德之说。已而自恩津。迁蓝浦。丁母夫人忧。哀毁过节。忧吉。转徙尚州以卒。时 哲宗癸丑也。距其生。 纯祖辛未。年四十三。朝廷始授缮工监役。闻其殁不施。季文,伯钦。时亦早殁。长汝年六十馀。穷居丹阳之山。李先生 哲考壬戌。名出贼招。被缧绁。今 上元年。第七十馀。始授台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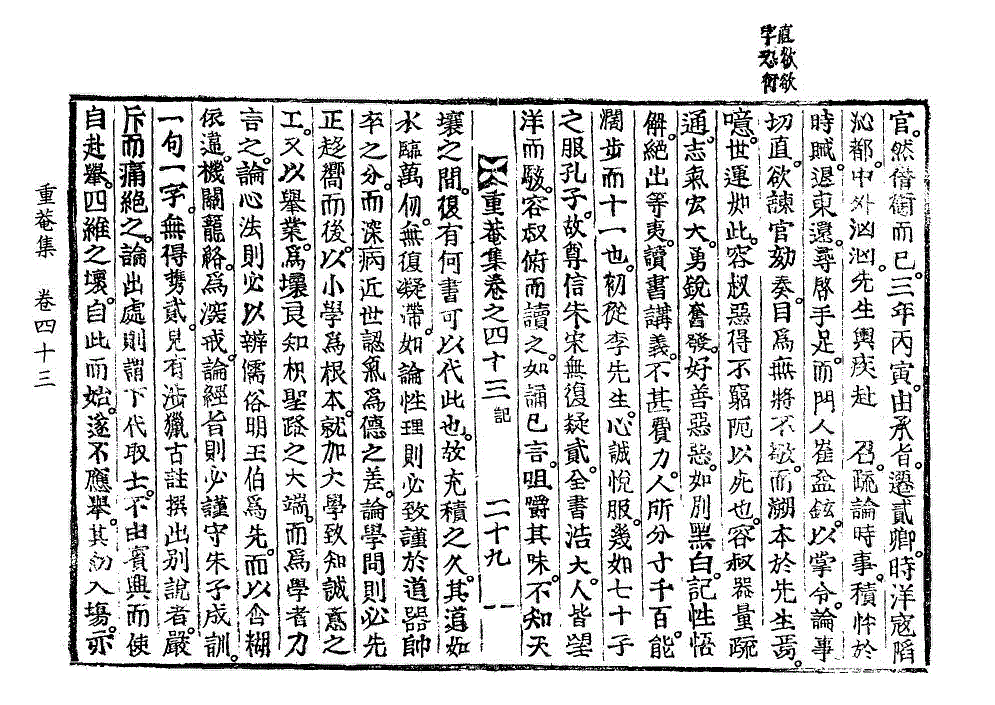 官。然借衔而已。三年丙寅。由承旨。迁贰卿。时洋寇陷沁都。中外汹汹。先生舆疾赴 召。疏论时事。积忤于时贼。退东还。寻启手足。而门人崔益铉。以掌令。论事切直。欲(直欲欲字恐衍)谏官劾奏。目为无将不敬。而溯本于先生焉。噫。世运如此。容叔恶得不穷阨以死也。容叔器量疏通。志气宏大。勇锐奋发。好善恶恶。如别黑白。记性悟解。绝出等夷。读书讲义。不甚费力。人所分寸千百。能阔步而十一也。初从李先生。心诚悦服。几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故尊信朱,宋无复疑贰。全书浩大。人皆望洋而骇。容叔俯而读之。如诵己言。咀嚼其味。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书可以代此也。故充积之久。其道如水临万仞。无复凝滞。如论性理则必致谨于道器帅卒之分。而深病近世认气为德之差。论学问则必先正趍向而后。以小学为根本。就加大学致知诚意之工。又以举业。为坏良知枳圣路之大端。而为学者力言之。论心法则必以辨儒俗明王伯为先。而以含糊依违。机关笼络。为深戒。论经旨则必谨守朱子成训。一句一字。无得携贰。见有涉猎古注撰出别说者。严斥而痛绝之。论出处则谓下代取士。不由宾兴而使自赴举。四维之坏。自此而始。遂不应举。其幼入场。亦
官。然借衔而已。三年丙寅。由承旨。迁贰卿。时洋寇陷沁都。中外汹汹。先生舆疾赴 召。疏论时事。积忤于时贼。退东还。寻启手足。而门人崔益铉。以掌令。论事切直。欲(直欲欲字恐衍)谏官劾奏。目为无将不敬。而溯本于先生焉。噫。世运如此。容叔恶得不穷阨以死也。容叔器量疏通。志气宏大。勇锐奋发。好善恶恶。如别黑白。记性悟解。绝出等夷。读书讲义。不甚费力。人所分寸千百。能阔步而十一也。初从李先生。心诚悦服。几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故尊信朱,宋无复疑贰。全书浩大。人皆望洋而骇。容叔俯而读之。如诵己言。咀嚼其味。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书可以代此也。故充积之久。其道如水临万仞。无复凝滞。如论性理则必致谨于道器帅卒之分。而深病近世认气为德之差。论学问则必先正趍向而后。以小学为根本。就加大学致知诚意之工。又以举业。为坏良知枳圣路之大端。而为学者力言之。论心法则必以辨儒俗明王伯为先。而以含糊依违。机关笼络。为深戒。论经旨则必谨守朱子成训。一句一字。无得携贰。见有涉猎古注撰出别说者。严斥而痛绝之。论出处则谓下代取士。不由宾兴而使自赴举。四维之坏。自此而始。遂不应举。其幼入场。亦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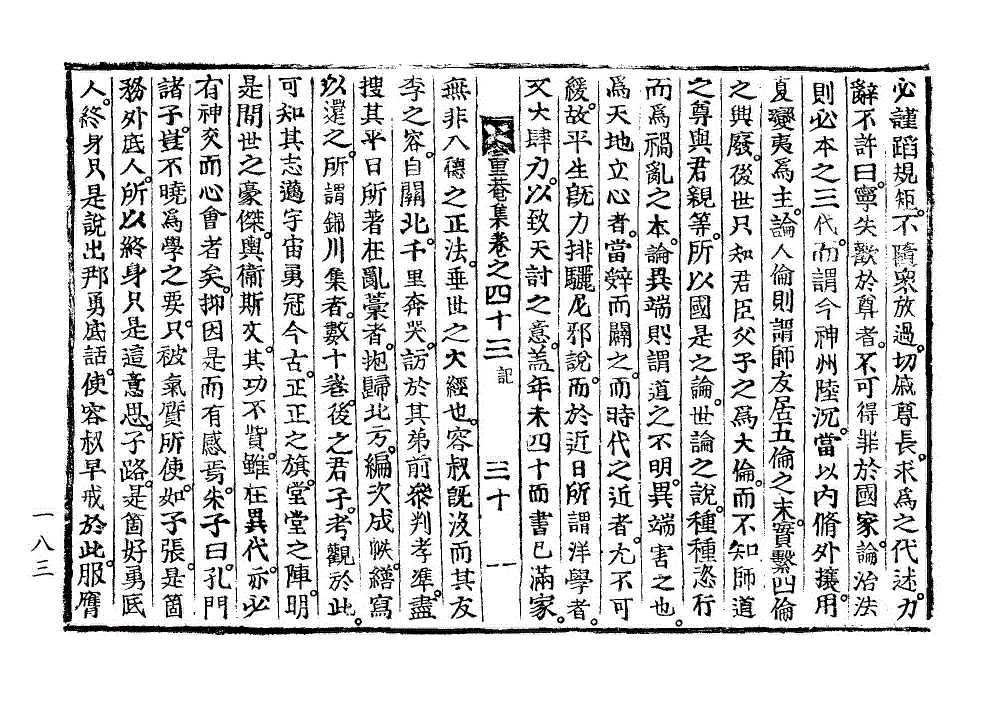 必谨蹈规矩。不随众放过。切戚尊长。求为之代述。力辞不许曰。宁失欢于尊者。不可得罪于国家。论治法则必本之三代。而谓今神州陆沉。当以内脩外攘。用夏变夷为主。论人伦则谓师友居五伦之末。实系四伦之兴废。后世只知君臣父子之为大伦。而不知师道之尊与君亲等。所以国是之论。世论之说。种种恣行而为祸乱之本。论异端则谓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为天地立心者。当辞而辟之。而时代之近者。尤不可缓。故平生既力排骊尼邪说。而于近日所谓洋学者。又大肆力。以致天讨之意。盖年未四十而书已满家。无非入德之正法。垂世之大经也。容叔既没而其友李之容。自关北。千里奔哭。访于其弟前参判孝准。尽搜其平日所著在乱藁者。抱归北方。编次成帙。缮写以还之。所谓锦川集者。数十卷。后之君子。考观于此。可知其志迈宇宙勇冠今古。正正之旗。堂堂之阵。明是间世之豪杰。舆卫斯文。其功不赀。虽在异代。亦必有神交而心会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朱子曰。孔门诸子。岂不晓为学之要。只被气质所使。如子张。是个务外底人。所以终身只是这意思。子路。是个好勇底人。终身只是说出那勇底话。使容叔早戒于此。服膺
必谨蹈规矩。不随众放过。切戚尊长。求为之代述。力辞不许曰。宁失欢于尊者。不可得罪于国家。论治法则必本之三代。而谓今神州陆沉。当以内脩外攘。用夏变夷为主。论人伦则谓师友居五伦之末。实系四伦之兴废。后世只知君臣父子之为大伦。而不知师道之尊与君亲等。所以国是之论。世论之说。种种恣行而为祸乱之本。论异端则谓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为天地立心者。当辞而辟之。而时代之近者。尤不可缓。故平生既力排骊尼邪说。而于近日所谓洋学者。又大肆力。以致天讨之意。盖年未四十而书已满家。无非入德之正法。垂世之大经也。容叔既没而其友李之容。自关北。千里奔哭。访于其弟前参判孝准。尽搜其平日所著在乱藁者。抱归北方。编次成帙。缮写以还之。所谓锦川集者。数十卷。后之君子。考观于此。可知其志迈宇宙勇冠今古。正正之旗。堂堂之阵。明是间世之豪杰。舆卫斯文。其功不赀。虽在异代。亦必有神交而心会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朱子曰。孔门诸子。岂不晓为学之要。只被气质所使。如子张。是个务外底人。所以终身只是这意思。子路。是个好勇底人。终身只是说出那勇底话。使容叔早戒于此。服膺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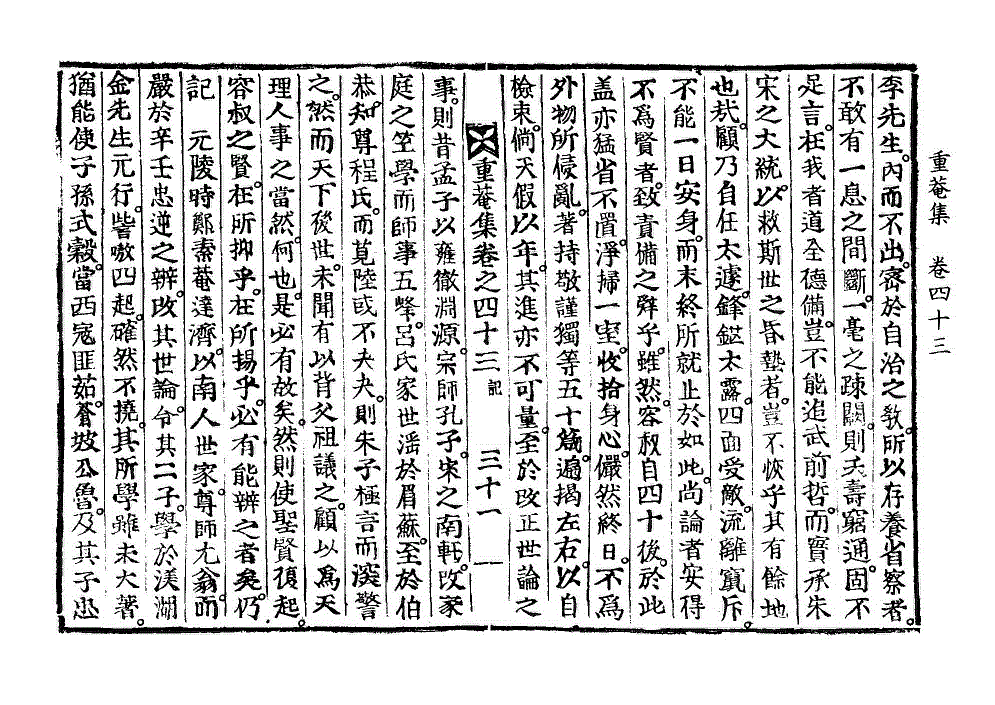 李先生。内而不出。密于自治之教。所以存养省察者。不敢有一息之间断。一毫之疏阙。则夭寿穷通。固不足言。在我者道全德备。岂不能追武前哲。而实承朱宋之大统。以救斯世之昏垫者。岂不恢乎其有馀地也哉。顾乃自任太遽。锋铓太露。四面受敌。流离窜斥。不能一日安身。而末终所就止于如此。尚论者安得不为贤者。致责备之辞乎。虽然。容叔自四十后。于此盖亦猛省不置。净扫一室。收拾身心。俨然终日。不为外物所侵乱。著持敬谨独等五十箴。遍揭左右。以自检束。倘天假以年。其进亦不可量。至于改正世论之事。则昔孟子以雍彻渊源。宗师孔子。宋之南轩。改家庭之竺学而师事五峰。吕氏家世淫于眉苏。至于伯恭。知尊程氏。而苋陆或不夬夬。则朱子极言而深警之。然而天下后世。未闻有以背父祖议之。顾以为天理人事之当然。何也。是必有故矣。然则使圣贤复起。容叔之贤。在所抑乎。在所扬乎。必有能辨之者矣。仍记 元陵时郑素庵达济。以南人世家。尊师尤翁。而严于辛壬忠逆之辨。改其世论。令其二子。学于渼湖金先生元行。訾嗷四起。确然不挠。其所学虽未大著。犹能使子孙式谷。当西寇匪茹。苍坡公鲁。及其子忠
李先生。内而不出。密于自治之教。所以存养省察者。不敢有一息之间断。一毫之疏阙。则夭寿穷通。固不足言。在我者道全德备。岂不能追武前哲。而实承朱宋之大统。以救斯世之昏垫者。岂不恢乎其有馀地也哉。顾乃自任太遽。锋铓太露。四面受敌。流离窜斥。不能一日安身。而末终所就止于如此。尚论者安得不为贤者。致责备之辞乎。虽然。容叔自四十后。于此盖亦猛省不置。净扫一室。收拾身心。俨然终日。不为外物所侵乱。著持敬谨独等五十箴。遍揭左右。以自检束。倘天假以年。其进亦不可量。至于改正世论之事。则昔孟子以雍彻渊源。宗师孔子。宋之南轩。改家庭之竺学而师事五峰。吕氏家世淫于眉苏。至于伯恭。知尊程氏。而苋陆或不夬夬。则朱子极言而深警之。然而天下后世。未闻有以背父祖议之。顾以为天理人事之当然。何也。是必有故矣。然则使圣贤复起。容叔之贤。在所抑乎。在所扬乎。必有能辨之者矣。仍记 元陵时郑素庵达济。以南人世家。尊师尤翁。而严于辛壬忠逆之辨。改其世论。令其二子。学于渼湖金先生元行。訾嗷四起。确然不挠。其所学虽未大著。犹能使子孙式谷。当西寇匪茹。苍坡公鲁。及其子忠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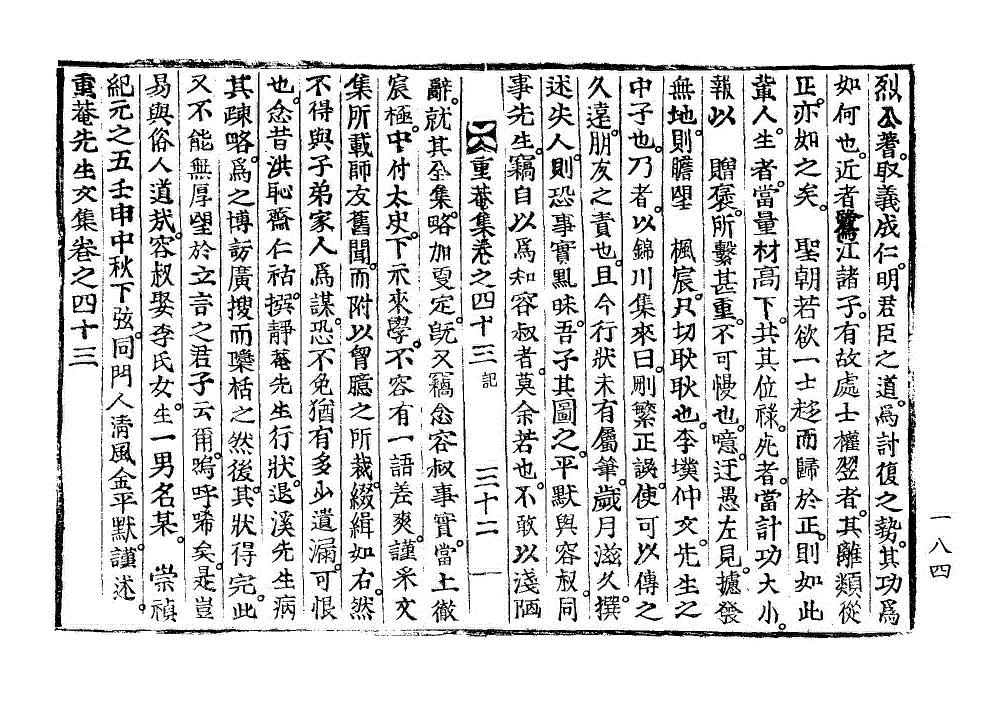 烈公蓍。取义成仁。明君臣之道。为讨复之势。其功为如何也。近者鹭江诸子。有故处士权翌者。其离类从正。亦如之矣。 圣朝若欲一士趍而归于正。则如此辈人。生者。当量材高下。共其位禄。死者。当计功大小。报以 赠褒。所系甚重。不可慢也。噫。迂愚左见。摅发无地。则瞻望 枫宸。只切耿耿也。李墣仲文。先生之中子也。乃者。以锦川集来曰。删繁正误。使可以传之久远。朋友之责也。且今行状未有属笔。岁月滋久。撰述失人。则恐事实䵝昧。吾子其图之。平默与容叔。同事先生。窃自以为知容叔者。莫余若也。不敢以浅陋辞。就其全集。略加更定。既又窃念容叔事实。当上彻宸极。中付太史。下示来学。不容有一语差爽。谨采文集所载师友旧闻。而附以胸臆之所裁。缀缉如右。然不得与子弟家人为谋。恐不免犹有多少遗漏。可恨也。念昔洪耻斋仁祜。撰静庵先生行状。退溪先生病其疏略。为之博访广搜而檃栝之然后。其状得完。此又不能无厚望于立言之君子云尔。呜呼唏矣。是岂易与俗人道哉。容叔娶李氏女。生一男名某。 崇祯纪元之五壬申中秋下弦。同门人清风金平默。谨述。
烈公蓍。取义成仁。明君臣之道。为讨复之势。其功为如何也。近者鹭江诸子。有故处士权翌者。其离类从正。亦如之矣。 圣朝若欲一士趍而归于正。则如此辈人。生者。当量材高下。共其位禄。死者。当计功大小。报以 赠褒。所系甚重。不可慢也。噫。迂愚左见。摅发无地。则瞻望 枫宸。只切耿耿也。李墣仲文。先生之中子也。乃者。以锦川集来曰。删繁正误。使可以传之久远。朋友之责也。且今行状未有属笔。岁月滋久。撰述失人。则恐事实䵝昧。吾子其图之。平默与容叔。同事先生。窃自以为知容叔者。莫余若也。不敢以浅陋辞。就其全集。略加更定。既又窃念容叔事实。当上彻宸极。中付太史。下示来学。不容有一语差爽。谨采文集所载师友旧闻。而附以胸臆之所裁。缀缉如右。然不得与子弟家人为谋。恐不免犹有多少遗漏。可恨也。念昔洪耻斋仁祜。撰静庵先生行状。退溪先生病其疏略。为之博访广搜而檃栝之然后。其状得完。此又不能无厚望于立言之君子云尔。呜呼唏矣。是岂易与俗人道哉。容叔娶李氏女。生一男名某。 崇祯纪元之五壬申中秋下弦。同门人清风金平默。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