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x 页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记
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0H 页
 敬窝记
敬窝记千古圣贤。论学问之要。不过曰敬而已矣。尧曰钦明。舜曰恭己。禹曰祇德。汤曰圣敬日跻。文王曰于缉熙敬止。孔子曰母不敬。至于洛闽诸先生。则所以释其义者。无复馀蕴矣。程夫子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以整齐严肃言之矣。其门人谢上蔡之语。则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和靖之语。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朱夫子一言以断之。则曰敬者。惟畏近之。又以扁其堂房夹室而为之记。为之箴。悉示其用力之方。至其门人黄文肃。诵夫子之雅言。则曰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其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其义理之实。呜呼。千古圣贤。论圣学之成始成终。不过如此。不学则已。如欲学焉。舍此宜无可者。友人结城张景仁。名其书室。为敬窝。命余为文以明之。盖华西李先生。自少为学。专主于敬。故操存日固。省察日密。而扩充日远。盖有以得其千圣相传之诀。景仁其宅相也。自八岁入学。所受于函丈者。无非是训。今其名言在玆。不亦宜哉。然尤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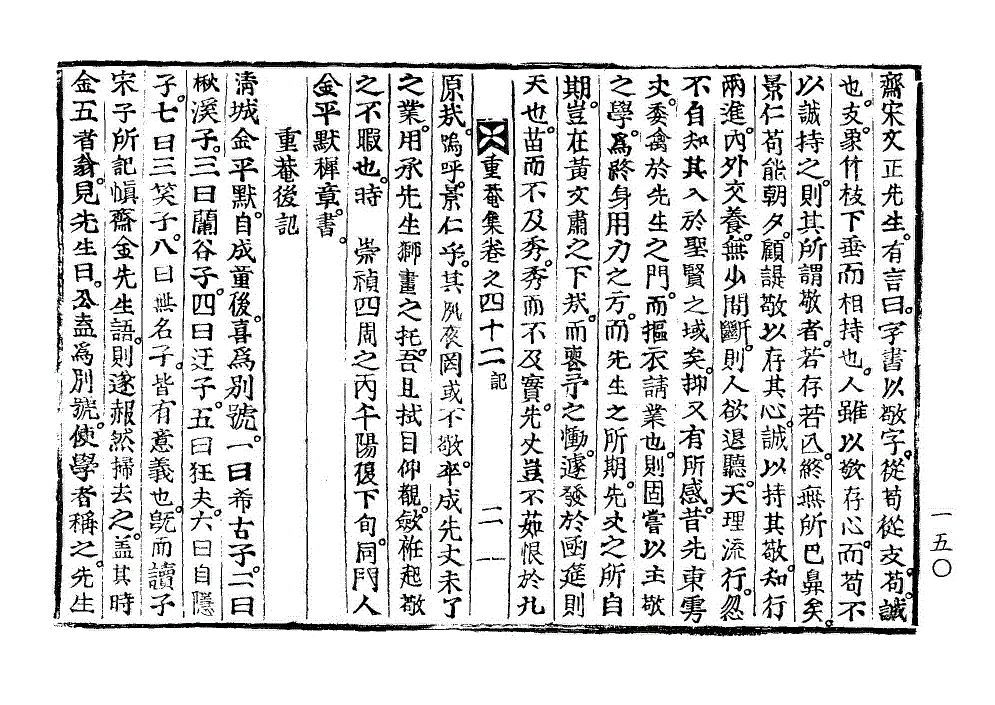 斋宋文正先生。有言曰。字书以敬字。从苟从支。苟。诚也。支。象竹枝下垂而相持也。人虽以敬存心。而苟不以诚持之。则其所谓敬者。若存若亡。终无所巴鼻矣。景仁苟能朝夕。顾諟敬以存其心。诚以持其敬。知行两进。内外交养。无少间断。则人欲退听。天理流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抑又有所感。昔先东雩丈。委禽于先生之门。而抠衣请业也。则固尝以主敬之学。为终身用力之方。而先生之所期。先丈之所自期。岂在黄文肃之下哉。而丧予之恸。遽发于函筵则天也。苗而不及秀。秀而不及实。先丈岂不茹恨于九原哉。呜呼。景仁乎。其夙夜罔或不敬。卒成先丈未了之业。用承先生狮画之托。吾且拭目仰睹。敛衽起敬之不暇也。时 崇祯四周之丙午阳复下旬。同门人金平默稚章。书。
斋宋文正先生。有言曰。字书以敬字。从苟从支。苟。诚也。支。象竹枝下垂而相持也。人虽以敬存心。而苟不以诚持之。则其所谓敬者。若存若亡。终无所巴鼻矣。景仁苟能朝夕。顾諟敬以存其心。诚以持其敬。知行两进。内外交养。无少间断。则人欲退听。天理流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抑又有所感。昔先东雩丈。委禽于先生之门。而抠衣请业也。则固尝以主敬之学。为终身用力之方。而先生之所期。先丈之所自期。岂在黄文肃之下哉。而丧予之恸。遽发于函筵则天也。苗而不及秀。秀而不及实。先丈岂不茹恨于九原哉。呜呼。景仁乎。其夙夜罔或不敬。卒成先丈未了之业。用承先生狮画之托。吾且拭目仰睹。敛衽起敬之不暇也。时 崇祯四周之丙午阳复下旬。同门人金平默稚章。书。重庵后记
清城金平默。自成童后。喜为别号。一曰希古子。二曰楸溪子。三曰兰谷子。四曰迂子。五曰狂夫。六曰自隐子。七曰三笑子。八曰无名子。皆有意义也。既而读子宋子所记慎斋金先生语。则遂赧然扫去之。盖其时金五者翁。见先生曰。公盍为别号。使学者称之。先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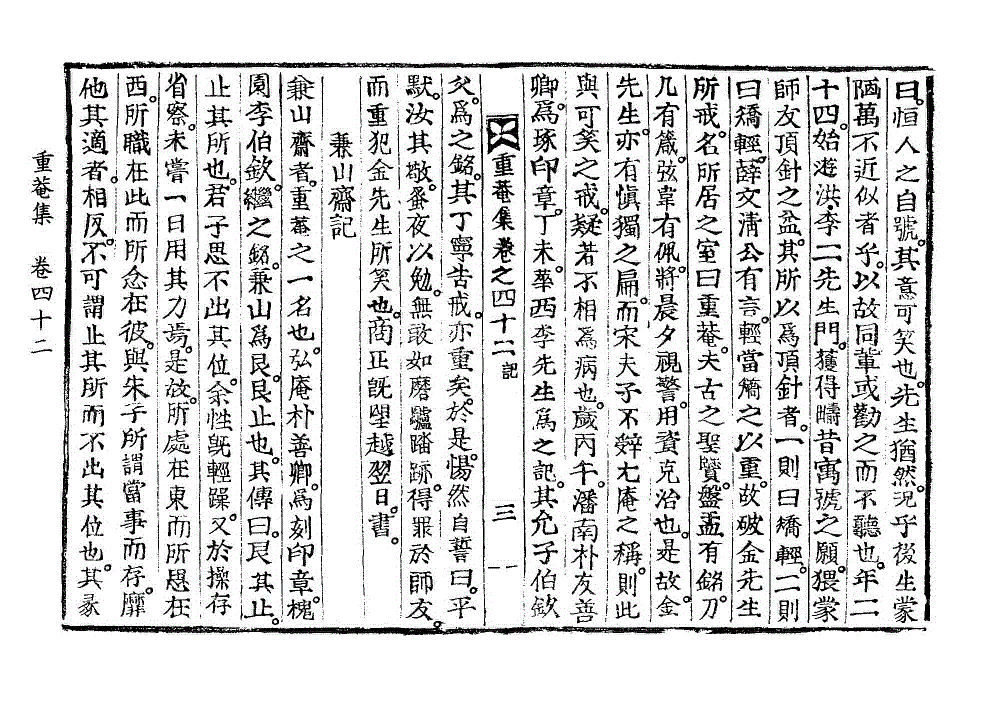 曰。恒人之自号。其意可笑也。先生犹然。况乎后生蒙陋万不近似者乎。以故同辈或劝之而不听也。年二十四。始游洪,李二先生门。获得畴昔寓号之愿。猥蒙师友顶针之益。其所以为顶针者。一则曰矫轻。二则曰矫轻。薛文清公有言。轻当矫之以重。故破金先生所戒。名所居之室曰重庵。夫古之圣贤。盘盂有铭。刀几有箴。弦韦有佩。将晨夕视警。用资克治也。是故。金先生。亦有慎独之扁。而宋夫子不辞尤庵之称。则此与可笑之戒。疑若不相为病也。岁丙午。潘南朴友善卿。为琢印章。丁未。华西李先生为之记。其允子伯钦父。为之铭。其丁宁告戒。亦重矣。于是。惕然自誓曰。平默。汝其敬。蚤夜以勉。无敢如磨驴踏迹。得罪于师友。而重犯金先生所笑也。商正既望越翌日。书。
曰。恒人之自号。其意可笑也。先生犹然。况乎后生蒙陋万不近似者乎。以故同辈或劝之而不听也。年二十四。始游洪,李二先生门。获得畴昔寓号之愿。猥蒙师友顶针之益。其所以为顶针者。一则曰矫轻。二则曰矫轻。薛文清公有言。轻当矫之以重。故破金先生所戒。名所居之室曰重庵。夫古之圣贤。盘盂有铭。刀几有箴。弦韦有佩。将晨夕视警。用资克治也。是故。金先生。亦有慎独之扁。而宋夫子不辞尤庵之称。则此与可笑之戒。疑若不相为病也。岁丙午。潘南朴友善卿。为琢印章。丁未。华西李先生为之记。其允子伯钦父。为之铭。其丁宁告戒。亦重矣。于是。惕然自誓曰。平默。汝其敬。蚤夜以勉。无敢如磨驴踏迹。得罪于师友。而重犯金先生所笑也。商正既望越翌日。书。兼山斋记
兼山斋者。重庵之一名也。弘庵朴善卿。为刻印章。槐园李伯钦。继之铭。兼山为艮。艮止也。其传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余性既轻躁。又于操存省察。未尝一日用其力焉。是故。所处在东而所思在西。所职在此而所念在彼。与朱子所谓当事而存。靡他其适者。相反。不可谓止其所而不出其位也。其彖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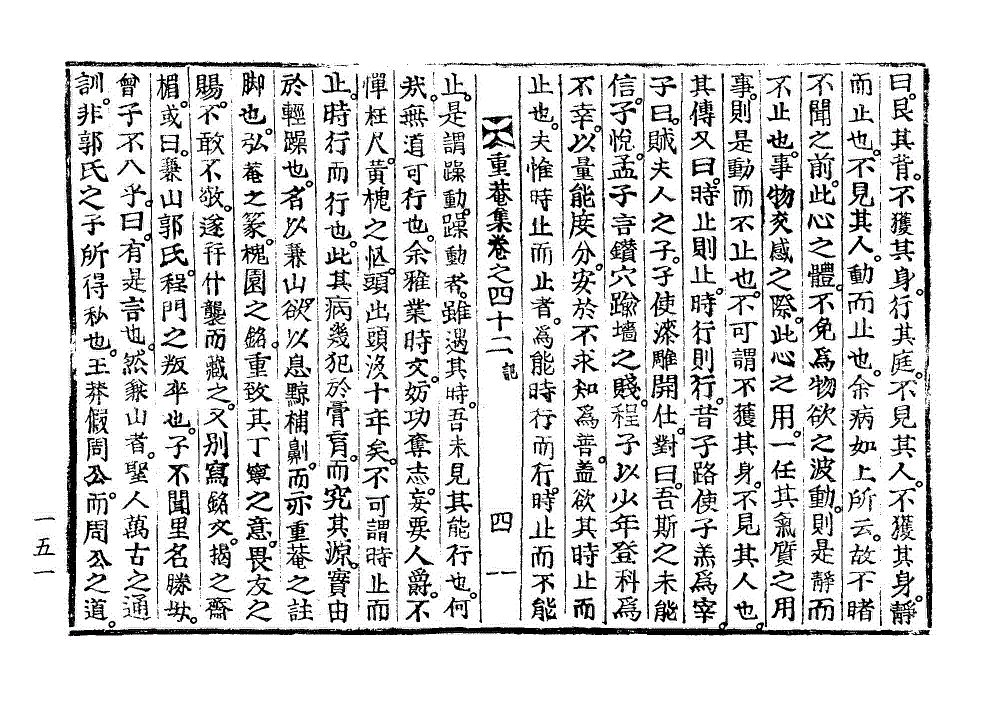 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不获其身。静而止也。不见其人。动而止也。余病如上所云。故不睹不闻之前。此心之体。不免为物欲之波动。则是静而不止也。事物交感之际。此心之用。一任其气质之用事。则是动而不止也。不可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其传又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昔子路使子羔为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孟子言钻穴踰墙之贱。程子以少年登科为不幸。以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为善。盖欲其时止而止也。夫惟时止而止者。为能时行而行。时止而不能止。是谓躁动。躁动者。虽遇其时。吾未见其能行也。何哉。无道可行也。余雅业时文。妨功夺志。妄要人爵。不惮枉尺。黄槐之忙。头出头没十年矣。不可谓时止而止。时行而行也。此其病几犯于膏肓。而究其源。实由于轻躁也。名以兼山。欲以息黥补劓。而亦重庵之注脚也。弘庵之篆。槐园之铭。重致其丁宁之意。畏友之赐。不敢不敬。遂并什袭而藏之。又别写铭文。揭之斋楣。或曰。兼山郭氏。程门之叛卒也。子不闻里名胜毋。曾子不入乎。曰。有是言也。然兼山者。圣人万古之通训。非郭氏之子所得私也。王莽假周公。而周公之道。
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不获其身。静而止也。不见其人。动而止也。余病如上所云。故不睹不闻之前。此心之体。不免为物欲之波动。则是静而不止也。事物交感之际。此心之用。一任其气质之用事。则是动而不止也。不可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其传又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昔子路使子羔为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孟子言钻穴踰墙之贱。程子以少年登科为不幸。以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为善。盖欲其时止而止也。夫惟时止而止者。为能时行而行。时止而不能止。是谓躁动。躁动者。虽遇其时。吾未见其能行也。何哉。无道可行也。余雅业时文。妨功夺志。妄要人爵。不惮枉尺。黄槐之忙。头出头没十年矣。不可谓时止而止。时行而行也。此其病几犯于膏肓。而究其源。实由于轻躁也。名以兼山。欲以息黥补劓。而亦重庵之注脚也。弘庵之篆。槐园之铭。重致其丁宁之意。畏友之赐。不敢不敬。遂并什袭而藏之。又别写铭文。揭之斋楣。或曰。兼山郭氏。程门之叛卒也。子不闻里名胜毋。曾子不入乎。曰。有是言也。然兼山者。圣人万古之通训。非郭氏之子所得私也。王莽假周公。而周公之道。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2H 页
 不可废。释家称牟尼。而仲尼之学。不可弃。诚若子言。郭忠孝。必衣服饮食矣。吾子将以为郭氏之所为也而废之乎。时 崇祯四丁未十二月癸亥。
不可废。释家称牟尼。而仲尼之学。不可弃。诚若子言。郭忠孝。必衣服饮食矣。吾子将以为郭氏之所为也而废之乎。时 崇祯四丁未十二月癸亥。亭亭亭记
濂溪周夫子。作爱莲说。谓莲花之君子者也。于是。天下之谈莲者。同辞而称君子。然以余观之。直周子之糟粕耳。若其所以谓之君子。而不容于不爱者。则未之或知也。盖君子之心。一于天理。故固未能离乎气矣。而亦未始为其所囿也。固未能外乎物矣。而亦未始为其所役也。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滓也者似之。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莲之濯乎清涟而不夭也者似之。君子敬以养其中。义以制乎外。故其静也虚。其动也直。体用一源。理事相须。精白纯粹。无少瑕翳。道传于久而无弊。德流于远而弥光。莲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而益清也者似之。君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莲之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者似之。此其所以谓君子而不容于不爱者。夫吾友任处士明老父。经纪茆亭于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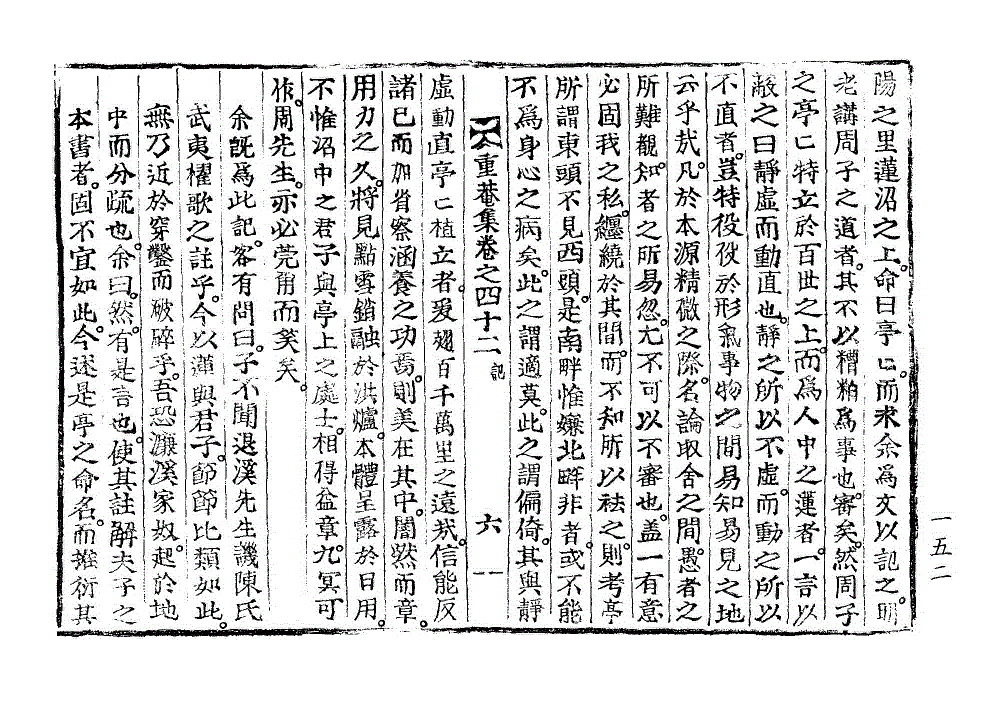 阳之里莲沼之上。命曰亭亭。而求余为文以记之。明老讲周子之道者。其不以糟粕为事也。审矣。然周子之亭亭特立于百世之上。而为人中之莲者。一言以蔽之曰静虚而动直也。静之所以不虚。而动之所以不直者。岂特役役于形气事物之间易知易见之地云乎哉。凡于本源精微之际。名论取舍之间。愚者之所难睹。知者之所易忽。尤不可以不审也。盖一有意必固我之私。缠绕于其间。而不知所以袪之。则考亭所谓东头不见西头。是南畔惟嫌北畔非者。或不能不为身心之病矣。此之谓适莫。此之谓偏倚。其与静虚动直亭亭植立者。爰翅百千万里之远哉。信能反诸己而加省察涵养之功焉。则美在其中。闇然而章。用力之久。将见点雪销融于洪炉。本体呈露于日用。不惟沼中之君子与亭上之处士。相得益章。九冥可作。周先生。亦必莞尔而笑矣。
阳之里莲沼之上。命曰亭亭。而求余为文以记之。明老讲周子之道者。其不以糟粕为事也。审矣。然周子之亭亭特立于百世之上。而为人中之莲者。一言以蔽之曰静虚而动直也。静之所以不虚。而动之所以不直者。岂特役役于形气事物之间易知易见之地云乎哉。凡于本源精微之际。名论取舍之间。愚者之所难睹。知者之所易忽。尤不可以不审也。盖一有意必固我之私。缠绕于其间。而不知所以袪之。则考亭所谓东头不见西头。是南畔惟嫌北畔非者。或不能不为身心之病矣。此之谓适莫。此之谓偏倚。其与静虚动直亭亭植立者。爰翅百千万里之远哉。信能反诸己而加省察涵养之功焉。则美在其中。闇然而章。用力之久。将见点雪销融于洪炉。本体呈露于日用。不惟沼中之君子与亭上之处士。相得益章。九冥可作。周先生。亦必莞尔而笑矣。余既为此记。客有问曰。子不闻退溪先生讥陈氏武夷棹歌之注乎。今以莲与君子。节节比类如此。无乃近于穿凿而破碎乎。吾恐濂溪家奴。起于地中而分疏也。余曰。然。有是言也。使其注解夫子之本书者。固不宜如此。今述是亭之命名。而推衍其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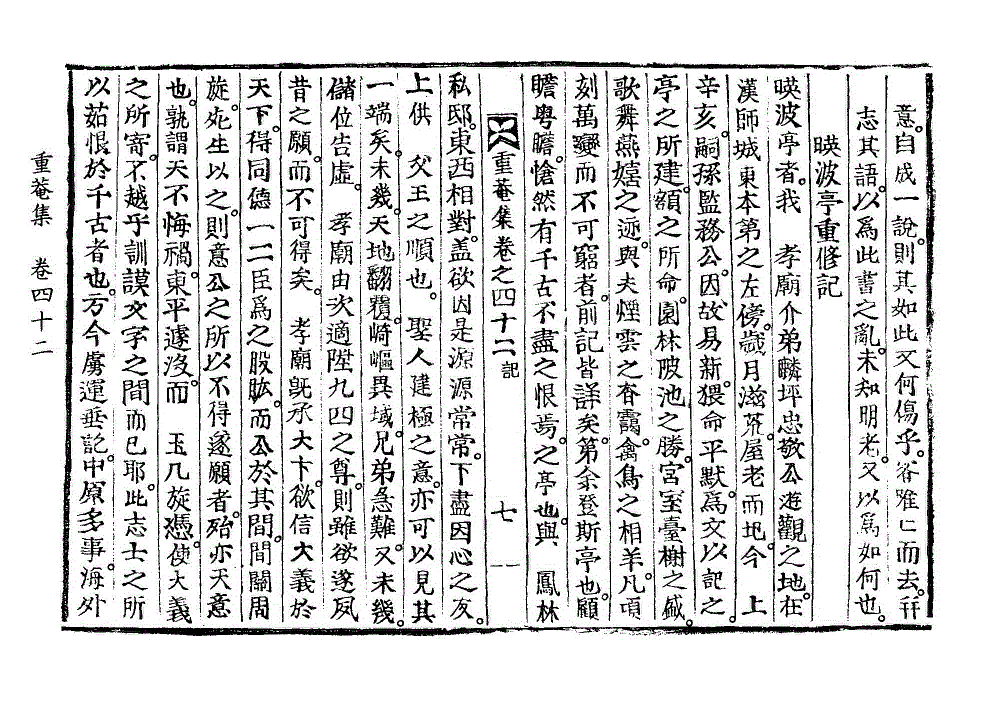 意。自成一说。则其如此又何伤乎。客唯唯而去。并志其语。以为此书之乱。未知明老。又以为如何也。
意。自成一说。则其如此又何伤乎。客唯唯而去。并志其语。以为此书之乱。未知明老。又以为如何也。映波亭重修记
映波亭者。我 孝庙介弟麟坪忠敬公游观之地。在汉师城东本第之左傍。岁月滋荒。屋老而圮。今 上辛亥。嗣孙监务公。因故易新。猥命平默。为文以记之。亭之所建。额之所命。园林陂池之胜。宫室台榭之盛歌舞燕嬉之迹。与夫烟云之杳霭。禽鸟之相羊。凡顷刻万变而不可穷者。前记皆详矣。第余登斯亭也。顾瞻粤瞻。怆然有千古不尽之恨焉。之亭也。与 凤林私邸。东西相对。盖欲因是源源常常。下尽因心之友。上供 父王之顺也。 圣人建极之意。亦可以见其一端矣。未几。天地翻覆。崎岖异域。兄弟急难。又未几。储位告虚。 孝庙由次适升九四之尊。则虽欲遂夙昔之愿。而不可得矣。 孝庙既承大卞。欲信大义于天下。得同德一二臣为之股肱。而公于其间。间关周旋。死生以之。则意公之所以不得遂愿者。殆亦天意也。孰谓天不悔祸。东平遽没。而 玉几旋凭。使大义之所寄。不越乎训谟文字之间而已耶。此志士之所以茹恨于千古者也。方今虏运垂讫。中原多事。海外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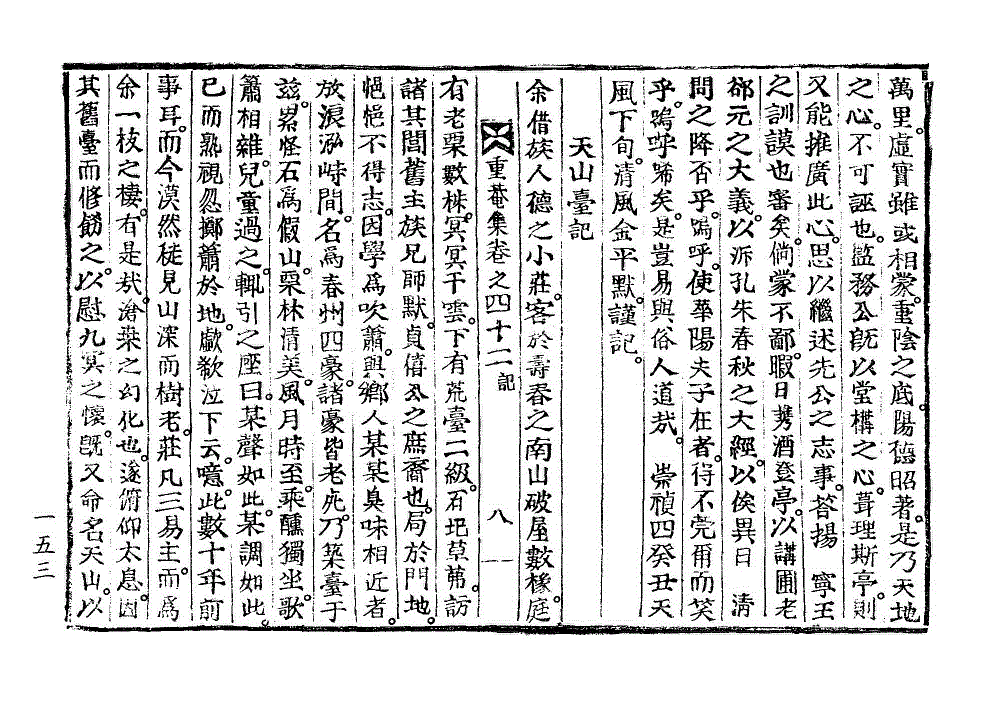 万里。虚实虽或相蒙。重阴之底。阳德昭著。是乃天地之心。不可诬也。监务公既以堂构之心。葺理斯亭。则又能推广此心。思以继述先公之志事。答扬 宁王之训谟也审矣。倘蒙不鄙。暇日携酒登亭。以讲圃老郤元之大义。以溯孔朱春秋之大经。以俟异日 清问之降否乎。呜呼。使华阳夫子在者。得不莞尔而笑乎。呜呼唏矣。是岂易与俗人道哉。 崇祯四癸丑天风下旬。清风金平默。谨记。
万里。虚实虽或相蒙。重阴之底。阳德昭著。是乃天地之心。不可诬也。监务公既以堂构之心。葺理斯亭。则又能推广此心。思以继述先公之志事。答扬 宁王之训谟也审矣。倘蒙不鄙。暇日携酒登亭。以讲圃老郤元之大义。以溯孔朱春秋之大经。以俟异日 清问之降否乎。呜呼。使华阳夫子在者。得不莞尔而笑乎。呜呼唏矣。是岂易与俗人道哉。 崇祯四癸丑天风下旬。清风金平默。谨记。天山台记
余借族人德之小庄。客于寿春之南山破屋数椽。庭有老栗数株。冥冥干云。下有荒台二级。石圮草茀。访诸其闾旧主族兄师默。贞僖公之庶裔也。局于门地。悒悒不得志。因学为吹箫。与乡人某某臭味相近者。放浪泓峙间。名为春州四豪。诸豪皆老死。乃筑台于玆。累怪石为假山。栗林清美。风月时至。乘醺独坐。歌箫相杂。儿童过之。辄引之座曰。某声如此。某调如此。已而熟视忽掷萧于地。歔欷泣下云。噫。此数十年前事耳。而今漠然徒见山深而树老。庄凡三易主。而为余一枝之栖。有是哉。沧桑之幻化也。遂俯仰太息。因其旧台而修饬之。以慰九冥之怀。既又命名天山。以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4H 页
 见肥遁之志。每日见光而起。整衣冠默坐。温绎洛建之书。向晚志倦体疲。缓步登台。引风雩之朋。奏反招之操。优哉游哉。亦足以乐而忘死矣。未知司命者。于我竟何如也。因是而有感焉。形器有限。道体无穷。天地之远也。一元则变形器之谓也。矧乎纪世时月之变哉。柏梁,铜雀。黄尘生焉。齐云,落星。感慨随之。崇恺之富焉而死。许史之贵焉而死。四君之豪焉而死。祝鮀宋朝之美且佞焉而死。朝为天下之歆艳。而暮为樵牧之咄嗟者何限。故无细大易难。无清浊高下。物之不可恃也如此。惟道之全体。得诸均畀之初。而具于方寸之间者。向也不幸为气拘欲蔽而失之。一日能克己以复之。则以之于家。以之于国。以之于天下。考诸三王。质诸鬼神。俟诸百世。先后天地而无不准是则可恃也。复之之术。洛建之书。备矣。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孔子引诗而叹曰。诚不以富。亦秖以异。其斯之谓欤。彼或以不可恃者。为毕生家计而不知返。得之不得。心以之䜣戚焉。其亦可悲也夫。其亦不知命也夫。
见肥遁之志。每日见光而起。整衣冠默坐。温绎洛建之书。向晚志倦体疲。缓步登台。引风雩之朋。奏反招之操。优哉游哉。亦足以乐而忘死矣。未知司命者。于我竟何如也。因是而有感焉。形器有限。道体无穷。天地之远也。一元则变形器之谓也。矧乎纪世时月之变哉。柏梁,铜雀。黄尘生焉。齐云,落星。感慨随之。崇恺之富焉而死。许史之贵焉而死。四君之豪焉而死。祝鮀宋朝之美且佞焉而死。朝为天下之歆艳。而暮为樵牧之咄嗟者何限。故无细大易难。无清浊高下。物之不可恃也如此。惟道之全体。得诸均畀之初。而具于方寸之间者。向也不幸为气拘欲蔽而失之。一日能克己以复之。则以之于家。以之于国。以之于天下。考诸三王。质诸鬼神。俟诸百世。先后天地而无不准是则可恃也。复之之术。洛建之书。备矣。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孔子引诗而叹曰。诚不以富。亦秖以异。其斯之谓欤。彼或以不可恃者。为毕生家计而不知返。得之不得。心以之䜣戚焉。其亦可悲也夫。其亦不知命也夫。孝妇咸平李氏旌闾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4L 页
 崇祯四丙子。抱川幼学宋贤鼎等上言。本县士人赵尚义妇咸平李氏。自髫龀。性于孝。甫十岁。其母有河鱼之崇。医云服温蜜。可立差也。家贫不得致。李氏日夜忧戚。忽有飞蜂一阵。集其家。受而畜之。其秋得以供母。已其疾。及归。推事舅姑。轻煖甘旨。靡不备具。舅尝病大朣则吮之。姑老食补不继则乳之。姑疾革。尝粪甜苦。炷香露祷。割指进血。竟得有喜。及遭艰。哀毁踰节。几致伤生。而鱼果之属。不入于口。自初终以至祥禫。祭奠亲自营办。如生如存。出于真诚。追远报本。老而不懈。斯诚王祥,庾娄,陈妇,唐媛之伦。合而为一人也。如或继朱子而作者。其序列于小学续编审矣。窃惟圣人之修道立教者。三纲也。五常也。是所谓人伦天理之至者。而于其中。又有最大而尤切者。所谓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是也。今李氏之行。原始要终。于其所谓大且切者。既无所憾。则其在 圣朝立教之道。宜施棹楔之典。以新一方之耳目。恐不容但已也。事下宗伯。宗伯因道查回 启。十二月。纯庙命旌其闾。子孙贫不得奉行。 当宁六年乙卯。棹楔成。荐绅章甫。作诗以咏歌之。曾孙镇衡。属县人金平默。追记其事如右。时丙辰三月少望日也。
崇祯四丙子。抱川幼学宋贤鼎等上言。本县士人赵尚义妇咸平李氏。自髫龀。性于孝。甫十岁。其母有河鱼之崇。医云服温蜜。可立差也。家贫不得致。李氏日夜忧戚。忽有飞蜂一阵。集其家。受而畜之。其秋得以供母。已其疾。及归。推事舅姑。轻煖甘旨。靡不备具。舅尝病大朣则吮之。姑老食补不继则乳之。姑疾革。尝粪甜苦。炷香露祷。割指进血。竟得有喜。及遭艰。哀毁踰节。几致伤生。而鱼果之属。不入于口。自初终以至祥禫。祭奠亲自营办。如生如存。出于真诚。追远报本。老而不懈。斯诚王祥,庾娄,陈妇,唐媛之伦。合而为一人也。如或继朱子而作者。其序列于小学续编审矣。窃惟圣人之修道立教者。三纲也。五常也。是所谓人伦天理之至者。而于其中。又有最大而尤切者。所谓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是也。今李氏之行。原始要终。于其所谓大且切者。既无所憾。则其在 圣朝立教之道。宜施棹楔之典。以新一方之耳目。恐不容但已也。事下宗伯。宗伯因道查回 启。十二月。纯庙命旌其闾。子孙贫不得奉行。 当宁六年乙卯。棹楔成。荐绅章甫。作诗以咏歌之。曾孙镇衡。属县人金平默。追记其事如右。时丙辰三月少望日也。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5H 页
 凤凰台记
凤凰台记有一麓自屏山。起起伏伏二十馀里。北至于昭阳下流。峗然而出。迥临貊国之野者曰凤凰台也。噫。凤凰不世出。仪于舜庭。鸣于岐山。咏于卷阿。东鲁之文明。孔圣叹其不至。出于颍川者。乃鹖雀也。寿州故貊国尔。胡然而来。以为名哉。吁知之矣。之台也。三山挟其左。二水经其前。于是乡人好事者。取青莲诗语。以名之尔。名而无实。或者疑其伪固也。然二水三山。流峙前左。则天造地设。亦非偊然。台无枳棘。骞噣舒翼。超乎莽苍之野。轩乎云霄之间。不经于世人之耳目。则是其隐而不见。又若有所待者存。然则之台也。非凤而凤尔。非凰而凰尔。有其实而得其名尔。何疑之有。吾闻凤凰。饥不啄粟。竹实之食。今东望数里曰有竹田。盖为凤凰食也。居人养粟而不养竹。何也。虞人之招。招大夫。犬马之畜。畜君子。决知其不可也。居人乎。其自今种竹而成行也。又闻凤凰非梧桐则不栖。台之左右。不可以不植梧桐也。虽然。居非丹山。孤而无类。可悲也已。然君子不云乎。凤凰之于飞鸟。类也。东去二十里。有鹤室。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则视凡飞鸟。其类又相近也。又东北十里。有凤仪之山。缥缈而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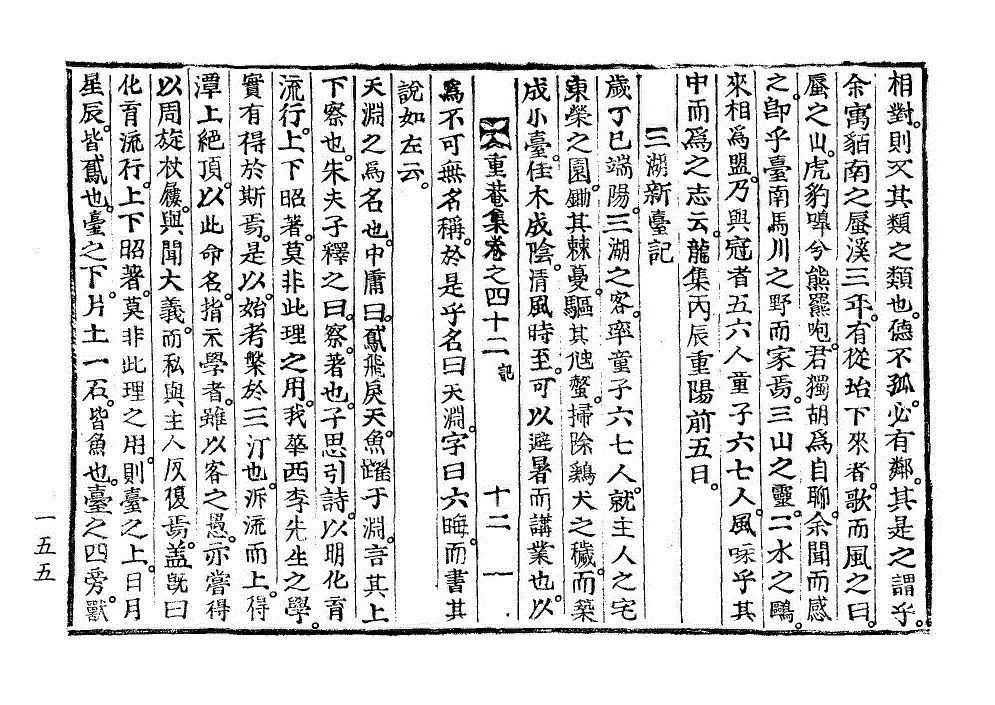 相对。则又其类之类也。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乎。余寓貊南之蜃溪三年。有从台下来者。歌而风之曰。蜃之山。虎豹嗥兮熊罴咆。君独胡为自聊。余闻而感之。即乎台南马川之野而家焉。三山之灵。二水之鸥。来相为盟。乃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风咏乎其中而为之志云。龙集丙辰重阳前五日。
相对。则又其类之类也。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乎。余寓貊南之蜃溪三年。有从台下来者。歌而风之曰。蜃之山。虎豹嗥兮熊罴咆。君独胡为自聊。余闻而感之。即乎台南马川之野而家焉。三山之灵。二水之鸥。来相为盟。乃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风咏乎其中而为之志云。龙集丙辰重阳前五日。三湖新台记
岁丁巳端阳。三湖之客。率童子六七人。就主人之宅东荣之园。锄其棘蔓。驱其虺螫。扫除鸡犬之秽。而筑成小台。佳木成阴。清风时至。可以避暑而讲业也。以为不可无名称。于是乎名曰天渊。字曰六晦。而书其说如左云。
天渊之为名也。中庸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朱夫子释之曰。察。著也。子思引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我华西李先生之学。实有得于斯焉。是以。始考槃于三汀也。溯流而上。得潭上绝顶。以此命名。指示学者。虽以客之愚。亦尝得以周旋杖屦。与闻大义。而私与主人反复焉。盖既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则台之上。日月星辰。皆鸢也。台之下。片土一石。皆鱼也。台之四旁。兽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6H 页
 声禽语之上下。烟光云影之散聚。松杉桃栗桑楮之森然成列。与夫山之樵。江之渔。原之牧。田之稼。朝夕往来。讴欧而笑语者。皆鸢鱼也。大则唐虞之揖逊。汤武之放伐。亦鸢鱼也。细则孔门之沂雩。程门之花柳。亦鸢鱼也。反之于吾身。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师友之伦。耳目鼻口手足四肢百骸之形。显而稠众之所能指。微而鬼神之所不能窥。无非所谓天之鸢而渊之鱼也。呜呼。玆所谓吾道一贯之者欤。我李先生夙兴夜寐。战兢临履。随事而省察之。期以袪夫一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量。内外始终。精粗钜细。天命无有所不行焉。既又推其所得而指示学者真切如此。今主与客。携手登亭。而童子六七人。从之讲业。则当仁不让之感。又亦胸中之鸢鱼也。于是乎名。呜呼。其亦顾名思义。而体之于身。验之于事。无令其鸢下而跃渊。鱼上而戾天。为台神所窃笑否乎。
声禽语之上下。烟光云影之散聚。松杉桃栗桑楮之森然成列。与夫山之樵。江之渔。原之牧。田之稼。朝夕往来。讴欧而笑语者。皆鸢鱼也。大则唐虞之揖逊。汤武之放伐。亦鸢鱼也。细则孔门之沂雩。程门之花柳。亦鸢鱼也。反之于吾身。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师友之伦。耳目鼻口手足四肢百骸之形。显而稠众之所能指。微而鬼神之所不能窥。无非所谓天之鸢而渊之鱼也。呜呼。玆所谓吾道一贯之者欤。我李先生夙兴夜寐。战兢临履。随事而省察之。期以袪夫一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量。内外始终。精粗钜细。天命无有所不行焉。既又推其所得而指示学者真切如此。今主与客。携手登亭。而童子六七人。从之讲业。则当仁不让之感。又亦胸中之鸢鱼也。于是乎名。呜呼。其亦顾名思义。而体之于身。验之于事。无令其鸢下而跃渊。鱼上而戾天。为台神所窃笑否乎。六晦之为字也。周颂曰。遵养时晦。易随之象曰。向晦入宴息。明夷之象曰。用晦而明。晦之义广矣大矣。以言乎四德。则利贞者晦也。而元亨生焉。以言乎四时。则收藏者晦也。而生养根焉。夫乾。其静也专晦也。故其动也直而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晦也。故其动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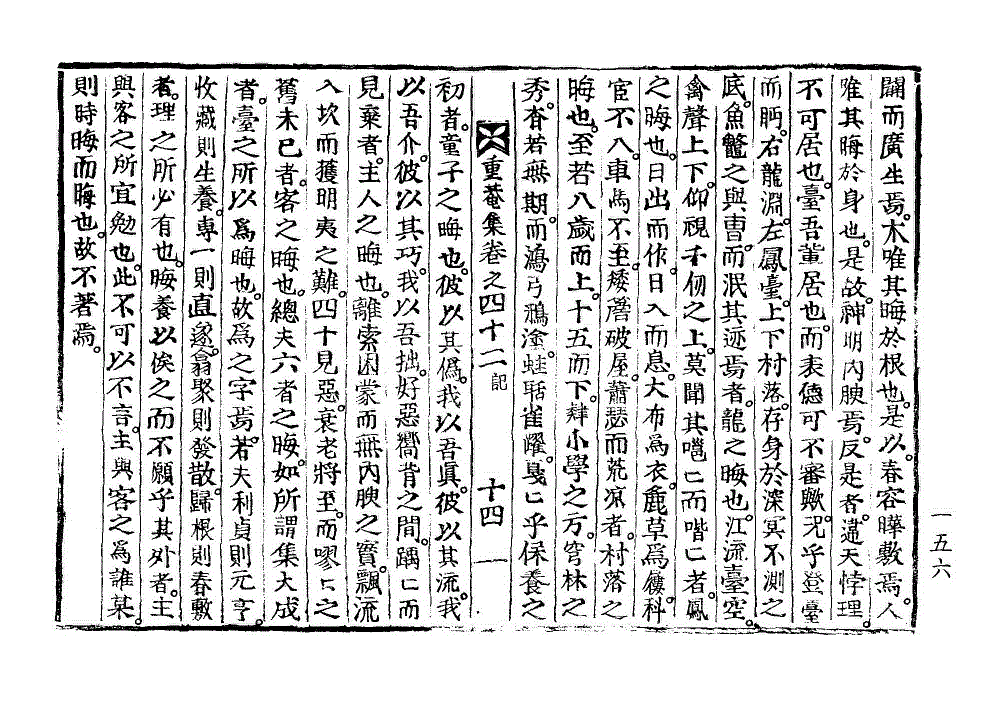 辟而广生焉。木唯其晦于根也。是以。春容晔敷焉。人唯其晦于身也。是故。神明内腴焉。反是者。违天悖理。不可居也。台吾辈居也。而表德可不审欤。况乎登台而眄。右龙渊。左凤台。上下村落。存身于深冥不测之底。鱼鳖之与曹。而泯其迹焉者。龙之晦也。江流台空。禽声上下。仰视千仞之上。莫闻其嗈嗈而喈喈者。凤之晦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布为衣。粗草为屦。科宦不入。车马不至。矮檐破屋。萧瑟而荒凉者。村落之晦也。至若八岁而上。十五而下。肄小学之方。穹林之秀。杳若无期。而鸿弓鸦涂。蛙聒雀跃。戛戛乎保养之初者。童子之晦也。彼以其伪。我以吾真。彼以其流。我以吾介。彼以其巧。我以吾拙。好恶向背之间。踽踽而见弃者。主人之晦也。离索困蒙而无内腴之实。飘流入坎而获明夷之难。四十见恶。衰老将至。而嘐嘐之旧未已者。客之晦也。总夫六者之晦。如所谓集大成者。台之所以为晦也。故为之字焉。若夫利贞则元亨。收藏则生养。专一则直遂。翕聚则发散。归根则春敷者。理之所必有也。晦养以俟之而不愿乎其外者。主与客之所宜勉也。此不可以不言。主与客之为谁某。则时晦而晦也。故不著焉。
辟而广生焉。木唯其晦于根也。是以。春容晔敷焉。人唯其晦于身也。是故。神明内腴焉。反是者。违天悖理。不可居也。台吾辈居也。而表德可不审欤。况乎登台而眄。右龙渊。左凤台。上下村落。存身于深冥不测之底。鱼鳖之与曹。而泯其迹焉者。龙之晦也。江流台空。禽声上下。仰视千仞之上。莫闻其嗈嗈而喈喈者。凤之晦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布为衣。粗草为屦。科宦不入。车马不至。矮檐破屋。萧瑟而荒凉者。村落之晦也。至若八岁而上。十五而下。肄小学之方。穹林之秀。杳若无期。而鸿弓鸦涂。蛙聒雀跃。戛戛乎保养之初者。童子之晦也。彼以其伪。我以吾真。彼以其流。我以吾介。彼以其巧。我以吾拙。好恶向背之间。踽踽而见弃者。主人之晦也。离索困蒙而无内腴之实。飘流入坎而获明夷之难。四十见恶。衰老将至。而嘐嘐之旧未已者。客之晦也。总夫六者之晦。如所谓集大成者。台之所以为晦也。故为之字焉。若夫利贞则元亨。收藏则生养。专一则直遂。翕聚则发散。归根则春敷者。理之所必有也。晦养以俟之而不愿乎其外者。主与客之所宜勉也。此不可以不言。主与客之为谁某。则时晦而晦也。故不著焉。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7H 页
 崔孝妇事行记
崔孝妇事行记孝妇。朔宁崔鼎镇之女也。归牛头士人郑思周。性于孝。事其姑曹氏。甚谨。曹氏寝疾。夜不解带。在视歇剧。大小便旋。躬亲洗涤。不以见人。十年如一日。曹氏性不食朝夕常馔。食辄生病。所嗜唯饼。家至贫。无以供。崔氏犹竭力常继。岁大饥。思周行四方乞怜知旧间。担负而供之。崔氏治红以足之。常置小甑。得米。皆作屑。令不乏。时问欲食与否。朝昼晨夕。每新蒸以进。糟糠不充。麻絮不掩。而姑极滋味。然常愉婉奉将。无愁怨叹息之意。闾里感而诵之。或有对面称之者。辄正色曰。你们无父母舅姑乎。是乃常职。何足称为。及没。哀毁踰礼。平日至行。皆类此。不可悉考。子锡膺夭逝。孙日承早孤。流离不得闻。今 上庚申。自南山。始返故居。闻农谣曰。嗣乃田事。崔饼是视。怪而问之。得事实如右。于是。乡人知其孝。君子曰。无诚不形。无幽不明。百年之久。神其章之。乡士好义者。议申状府伯。以为旌闾地也。
香下记
甄城柳季昭氏。因其所居。𤗐书室为香下。求余文甚勤。香之山川。无泓峙殊绝。无佳木异石珍禽奇花及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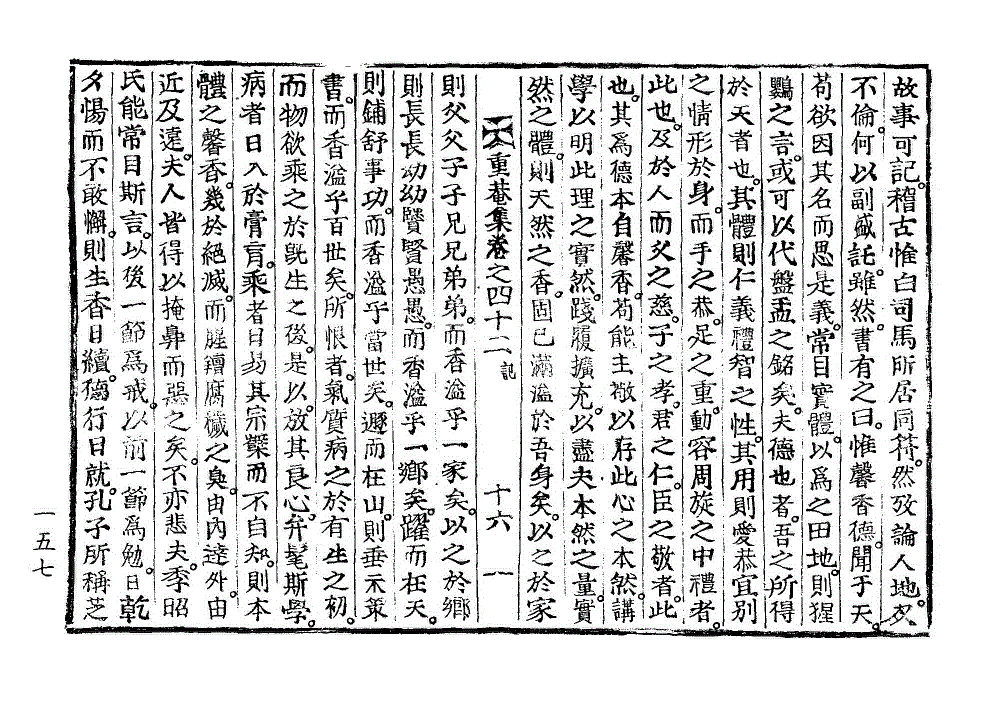 故事可记。稽古惟白司马所居同符。然考论人地。又不伦。何以副盛托。虽然。书有之曰。惟馨香德。闻于天。苟欲因其名而思是义。常目实体。以为之田地。则猩鹦之言。或可以代盘盂之铭矣。夫德也者。吾之所得于天者也。其体则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爱恭宜别之情形于身。而手之恭。足之重。动容周旋之中礼者。此也。及于人而父之慈。子之孝。君之仁。臣之敬者。此也。其为德本自馨香。苟能主敬以存此心之本然。讲学以明此理之实然。践履扩充。以尽夫本然之量。实然之体。则天然之香。固已满溢于吾身矣。以之于家则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香溢乎一家矣。以之于乡则长长幼幼贤贤愚愚。而香溢乎一乡矣。跃而在天。则铺舒事功。而香溢乎当世矣。遁而在山。则垂示策书。而香溢乎百世矣。所恨者。气质病之于有生之初。而物欲乘之于既生之后。是以。放其良心。弁髦斯学。病者日入于膏肓。乘者日易其宗蘖而不自知。则本体之馨香。几于绝灭。而腥膻腐秽之臭。由内达外。由近及远。夫人皆得以掩鼻而恶之矣。不亦悲夫。季昭氏能常目斯言。以后一节为戒。以前一节为勉。日乾夕惕而不敢懈。则生香日续。德行日就。孔子所称芝
故事可记。稽古惟白司马所居同符。然考论人地。又不伦。何以副盛托。虽然。书有之曰。惟馨香德。闻于天。苟欲因其名而思是义。常目实体。以为之田地。则猩鹦之言。或可以代盘盂之铭矣。夫德也者。吾之所得于天者也。其体则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爱恭宜别之情形于身。而手之恭。足之重。动容周旋之中礼者。此也。及于人而父之慈。子之孝。君之仁。臣之敬者。此也。其为德本自馨香。苟能主敬以存此心之本然。讲学以明此理之实然。践履扩充。以尽夫本然之量。实然之体。则天然之香。固已满溢于吾身矣。以之于家则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香溢乎一家矣。以之于乡则长长幼幼贤贤愚愚。而香溢乎一乡矣。跃而在天。则铺舒事功。而香溢乎当世矣。遁而在山。则垂示策书。而香溢乎百世矣。所恨者。气质病之于有生之初。而物欲乘之于既生之后。是以。放其良心。弁髦斯学。病者日入于膏肓。乘者日易其宗蘖而不自知。则本体之馨香。几于绝灭。而腥膻腐秽之臭。由内达外。由近及远。夫人皆得以掩鼻而恶之矣。不亦悲夫。季昭氏能常目斯言。以后一节为戒。以前一节为勉。日乾夕惕而不敢懈。则生香日续。德行日就。孔子所称芝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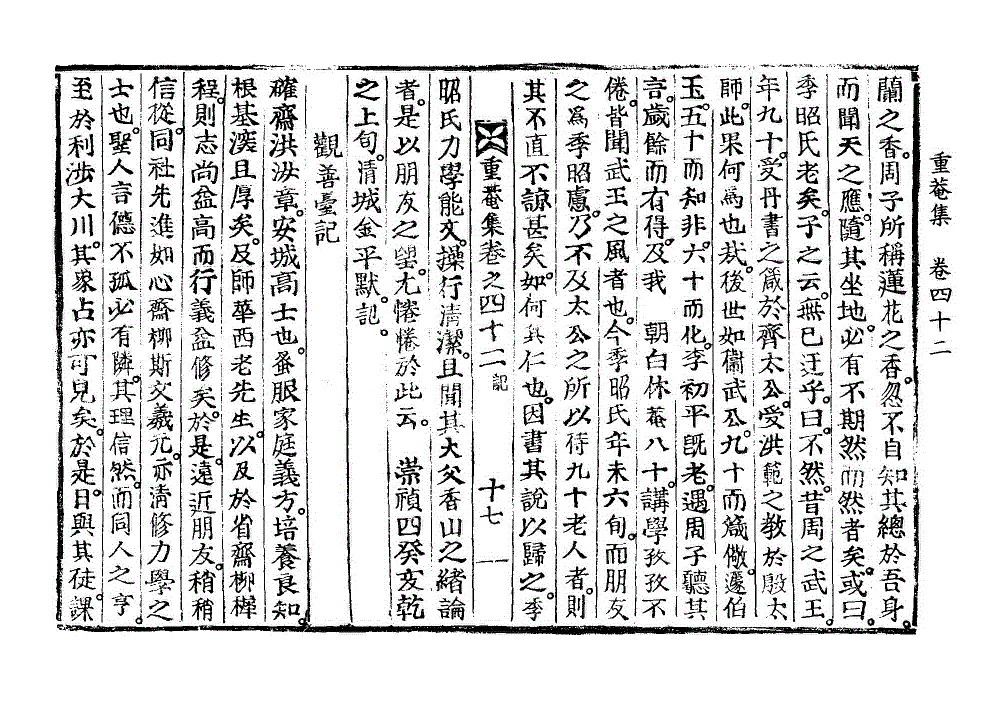 兰之香。周子所称莲花之香。忽不自知其总于吾身。而闻天之应。随其坐地。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曰。季昭氏老矣。子之云。无已迂乎。曰。不然。昔周之武王。年九十。受丹书之箴于齐太公。受洪范之教于殷太师。此果何为也哉。后世如卫武公。九十而箴儆。蘧伯玉。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李初平既老。遇周子听其言。岁馀而有得。及我 朝白休庵八十。讲学孜孜不倦。皆闻武王之风者也。今季昭氏年未六旬。而朋友之为季昭虑。乃不及太公之所以待九十老人者。则其不直不谅甚矣。如何其仁也。因书其说以归之。季昭氏力学能文。操行清洁。且闻其大父香山之绪论者。是以朋友之望。尤惓惓于此云。 崇祯四癸亥乾之上旬。清城金平默。记。
兰之香。周子所称莲花之香。忽不自知其总于吾身。而闻天之应。随其坐地。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曰。季昭氏老矣。子之云。无已迂乎。曰。不然。昔周之武王。年九十。受丹书之箴于齐太公。受洪范之教于殷太师。此果何为也哉。后世如卫武公。九十而箴儆。蘧伯玉。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李初平既老。遇周子听其言。岁馀而有得。及我 朝白休庵八十。讲学孜孜不倦。皆闻武王之风者也。今季昭氏年未六旬。而朋友之为季昭虑。乃不及太公之所以待九十老人者。则其不直不谅甚矣。如何其仁也。因书其说以归之。季昭氏力学能文。操行清洁。且闻其大父香山之绪论者。是以朋友之望。尤惓惓于此云。 崇祯四癸亥乾之上旬。清城金平默。记。观善台记
确斋洪汝章。安城高士也。蚤服家庭义方。培养良知。根基深且厚矣。及师华西老先生。以及于省斋柳稚程。则志尚益高而行义益修矣。于是。远近朋友。稍稍信从。同社先进如心斋柳斯文羲元。亦清修力学之士也。圣人言德不孤必有邻。其理信然。而同人之亨。至于利涉大川。其象占亦可见矣。于是。日与其徒。课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8L 页
 学有程。因就社园。除地筑台。会讲于斯。习饮射,读法,士相见诸礼于斯。而名之曰观善。谓贱仆亦尝在丽泽之末。踵门而请记焉。仆敬诺而不辞。汝章去。或有问于仆者曰。程子谓朋友讲习。更莫如相观而善。二者。当相须交济而不可偏重者也。程子之意于此。若有所抑扬焉。何哉。仆应之曰。君子之教人也。因人变化而不拘于一定。程子之言。盖为偏于讲习者而发也。曰。然则此友之名是台也。亦程子之意欤。仆曰。固然矣。以吾观之。朋友讲明在此友。可急而不可缓。若或悠泛不省。而遽欲归重于观善。则朋友之忧。窃恐其无已也。诗云。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贱仆之于此友。其忠爱之深。岂下于人。顾惟无状。不能信在言前。则恐犯尚口之戒。是以次且而不敢有言。此则贱仆之罪也。曰。可得闻欤。仆曰。同人之象。既言足以听闻。则又必类族辨物。而大师以克。可以致亨。而涉乎大川。无所不利矣。不然而含糊苟且。优柔不断。安于系宗升陵之象占而不自知焉。则理所不亨。何事可济也。是故。朱子后圣也。其尚论前哲。推尊子思,孟子之刚毅立脚。而病夫仲弓之偏于淳笃其自为。则阴阳义利邪正淑慝之际。好恶向背。如一剑两段。疑似必辨。
学有程。因就社园。除地筑台。会讲于斯。习饮射,读法,士相见诸礼于斯。而名之曰观善。谓贱仆亦尝在丽泽之末。踵门而请记焉。仆敬诺而不辞。汝章去。或有问于仆者曰。程子谓朋友讲习。更莫如相观而善。二者。当相须交济而不可偏重者也。程子之意于此。若有所抑扬焉。何哉。仆应之曰。君子之教人也。因人变化而不拘于一定。程子之言。盖为偏于讲习者而发也。曰。然则此友之名是台也。亦程子之意欤。仆曰。固然矣。以吾观之。朋友讲明在此友。可急而不可缓。若或悠泛不省。而遽欲归重于观善。则朋友之忧。窃恐其无已也。诗云。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贱仆之于此友。其忠爱之深。岂下于人。顾惟无状。不能信在言前。则恐犯尚口之戒。是以次且而不敢有言。此则贱仆之罪也。曰。可得闻欤。仆曰。同人之象。既言足以听闻。则又必类族辨物。而大师以克。可以致亨。而涉乎大川。无所不利矣。不然而含糊苟且。优柔不断。安于系宗升陵之象占而不自知焉。则理所不亨。何事可济也。是故。朱子后圣也。其尚论前哲。推尊子思,孟子之刚毅立脚。而病夫仲弓之偏于淳笃其自为。则阴阳义利邪正淑慝之际。好恶向背。如一剑两段。疑似必辨。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9H 页
 毫釐必察。未尝少有依违因仍之私。或有以利害祸福怵之者。则曰使我壁立万仞。岂不为吾道之光。其临终而授门人真诀。则曰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则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此乃同人亨利之道。而并其邻受福者也。易曰。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朱子曰。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天下万事皆好。此之谓也。此所谓可急不可缓。而贱仆之忉忉不置者也。噫。此岂狂疾痴呆而然耶。抑亦出于情性之正者耶。必有能辨之者矣。问者举手而谢曰。问一得四。闻君子教人之道。闻君子爱人以德之仁。闻君子量己慎言之智。又闻朱子之学。正得天地之性。圣人之心。学者少不著眼。则然疑之间。顾眄之顷。缠绕于私障。坠堕于榛棘而观善。又不足以救之也。问者退。悉次其语而藏之巾笥矣。忠爱终胜。不得忍住。遂双擎而进之。呜呼。汝章乎。其亦有以谅之也。 崇祯五周上章敦牂之孟夏。清风金平默。记。
毫釐必察。未尝少有依违因仍之私。或有以利害祸福怵之者。则曰使我壁立万仞。岂不为吾道之光。其临终而授门人真诀。则曰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则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此乃同人亨利之道。而并其邻受福者也。易曰。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朱子曰。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天下万事皆好。此之谓也。此所谓可急不可缓。而贱仆之忉忉不置者也。噫。此岂狂疾痴呆而然耶。抑亦出于情性之正者耶。必有能辨之者矣。问者举手而谢曰。问一得四。闻君子教人之道。闻君子爱人以德之仁。闻君子量己慎言之智。又闻朱子之学。正得天地之性。圣人之心。学者少不著眼。则然疑之间。顾眄之顷。缠绕于私障。坠堕于榛棘而观善。又不足以救之也。问者退。悉次其语而藏之巾笥矣。忠爱终胜。不得忍住。遂双擎而进之。呜呼。汝章乎。其亦有以谅之也。 崇祯五周上章敦牂之孟夏。清风金平默。记。汉浦书社记
史记世家。楚昭王。欲以书社地封孔子。饶氏谓书社。今之书会也。封之于此。欲以养其徒也。又古者乡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59L 页
 生殁则祭于社。是其为师长教授生徒讲习之所。其来远矣。龙门之北。有汉阳浦。地僻而俗朴。且距静庵赵文正迷源书院。隔一带涧水。先师华西李先生。檗溪学舍二十里而强。李先生既老。而其高弟省斋柳稚程隐居。讲道于其中。今 上丙寅。平默亦自嘉陵。迁居浦南之大谷。仍相与丽泽。粗偿其夙昔共修之约。稚程以生徒坌集。而堂室无可容者。与金仁叟诸人。议鸠财建舍。戊辰。李先生捐皋比。己巳春。迷源书院以 朝令毁。而此舍适成于其时。噫。岂程夫子所谓阳变于上。则复生于下。无间可容息者。于此。亦见其一端也欤。稚程率徒友以告圣师。既又名其正堂曰主一。其两夹室。左曰博约。右曰克复。左室之东牖曰咏柏。右室之西牖曰山仰。为之文以明其义意。又筑台于东荣之庭。为习礼之地。总而名之曰汉浦书社。生徒远来者。馆接于此。每岁四孟。每月三旬。必设一会。稚程以平默。尝僭据非坐。以记文见属。盖其意非区区焉。备社中掌故。将以揭之堂颜。使朝夕于此者。仰而读之。切己警励。而不至于堕空落虚也。此其片片赤心。可质神明也。昔者。闻诸李先生曰。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贾。是也。士。食德者也。农。食力者也。工。
生殁则祭于社。是其为师长教授生徒讲习之所。其来远矣。龙门之北。有汉阳浦。地僻而俗朴。且距静庵赵文正迷源书院。隔一带涧水。先师华西李先生。檗溪学舍二十里而强。李先生既老。而其高弟省斋柳稚程隐居。讲道于其中。今 上丙寅。平默亦自嘉陵。迁居浦南之大谷。仍相与丽泽。粗偿其夙昔共修之约。稚程以生徒坌集。而堂室无可容者。与金仁叟诸人。议鸠财建舍。戊辰。李先生捐皋比。己巳春。迷源书院以 朝令毁。而此舍适成于其时。噫。岂程夫子所谓阳变于上。则复生于下。无间可容息者。于此。亦见其一端也欤。稚程率徒友以告圣师。既又名其正堂曰主一。其两夹室。左曰博约。右曰克复。左室之东牖曰咏柏。右室之西牖曰山仰。为之文以明其义意。又筑台于东荣之庭。为习礼之地。总而名之曰汉浦书社。生徒远来者。馆接于此。每岁四孟。每月三旬。必设一会。稚程以平默。尝僭据非坐。以记文见属。盖其意非区区焉。备社中掌故。将以揭之堂颜。使朝夕于此者。仰而读之。切己警励。而不至于堕空落虚也。此其片片赤心。可质神明也。昔者。闻诸李先生曰。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贾。是也。士。食德者也。农。食力者也。工。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0H 页
 食技者也。贾。食利者也。是故。士以养德为职。农以勤力为职。工以殚技为职。贾以殖货为职。不由此四者而食者。先儒谓之奸民。奸民者。不容于先王之世。夫堕于农工者。民斯为下矣。不足言也。出入书社而在讲习之列。则是有士之名矣。有士之名。不幸而无养德之实。则失其所以为士矣。失其所以为士而犹且食之。则先儒当以为如何。先王当以为如何。堕空落虚。其效至此。深可惧也。然则何如。斯可以养德矣。亦曰。主一以立其本。博文以致其知。克己以除其沴疾。约礼以复其本然。此其梗槩。已具于省斋之文。尧舜文武之所以为天下君。孔孟程朱之所以为万世师。其传授心法。正在于此。而赵李二先生之所以嘉惠于此邦者。实出于一辙。则味柏山仰之命名。又见其寄意不偶然而已。此在诸君子。依文按本。羹墙奋勉而已。无他说也。此厥不听。随行逐队。悠悠旋旋。师友之教。如水投石。外诱之来。其甘如蔗。弹冠入社。则稍可以瞒人。纳履出门。则复还其本分。日往月来。了无尺寸之益。则所谓堕空落虚之效。虽不欲索言。而即此书社花果草木。莫不带累。诸君子岂有是耶。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诸君子其亦忿之。仁叟社中老
食技者也。贾。食利者也。是故。士以养德为职。农以勤力为职。工以殚技为职。贾以殖货为职。不由此四者而食者。先儒谓之奸民。奸民者。不容于先王之世。夫堕于农工者。民斯为下矣。不足言也。出入书社而在讲习之列。则是有士之名矣。有士之名。不幸而无养德之实。则失其所以为士矣。失其所以为士而犹且食之。则先儒当以为如何。先王当以为如何。堕空落虚。其效至此。深可惧也。然则何如。斯可以养德矣。亦曰。主一以立其本。博文以致其知。克己以除其沴疾。约礼以复其本然。此其梗槩。已具于省斋之文。尧舜文武之所以为天下君。孔孟程朱之所以为万世师。其传授心法。正在于此。而赵李二先生之所以嘉惠于此邦者。实出于一辙。则味柏山仰之命名。又见其寄意不偶然而已。此在诸君子。依文按本。羹墙奋勉而已。无他说也。此厥不听。随行逐队。悠悠旋旋。师友之教。如水投石。外诱之来。其甘如蔗。弹冠入社。则稍可以瞒人。纳履出门。则复还其本分。日往月来。了无尺寸之益。则所谓堕空落虚之效。虽不欲索言。而即此书社花果草木。莫不带累。诸君子岂有是耶。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诸君子其亦忿之。仁叟社中老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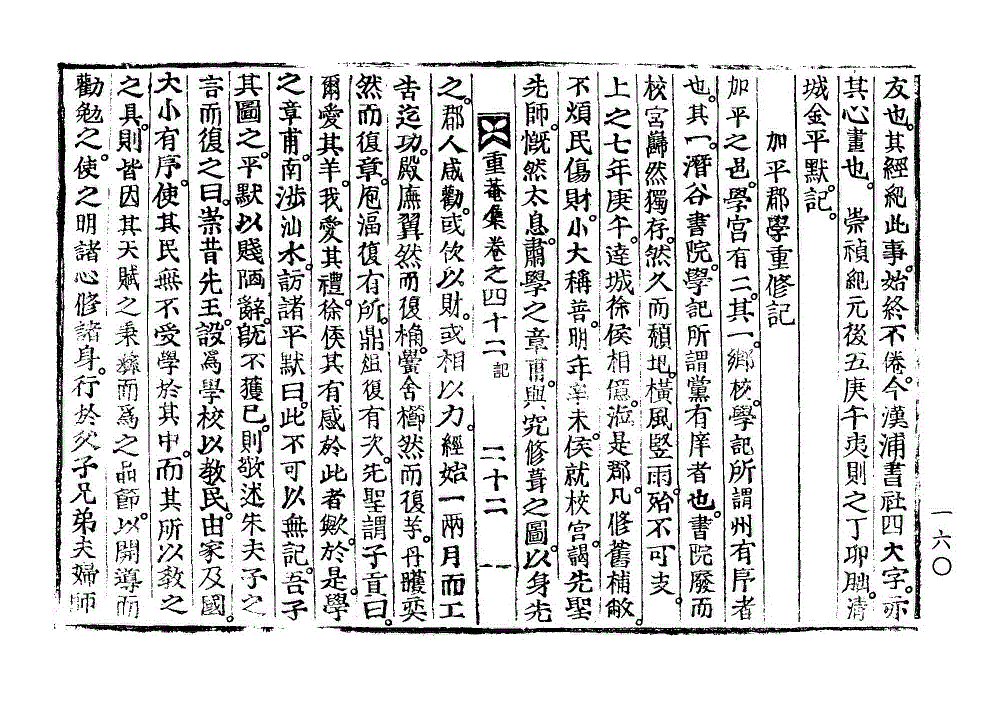 友也。其经纪此事。始终不倦。今汉浦书社四大字。亦其心画也。 崇祯纪元后五庚午夷则之丁卯朏。清城金平默。记。
友也。其经纪此事。始终不倦。今汉浦书社四大字。亦其心画也。 崇祯纪元后五庚午夷则之丁卯朏。清城金平默。记。加平郡学重修记
加平之邑。学宫有二。其一。乡校。学记所谓州有序者也。其一。潜谷书院。学记所谓党有庠者也。书院废而校宫岿然独存。然久而颓圮。横风竖雨。殆不可支。 上之七年庚午。达城徐侯相亿。涖是郡。凡修旧补敝。不烦民伤财。小大称善。明年辛未。侯就校宫。谒先圣先师。慨然太息。肃学之章甫。与究修葺之图。以身先之。郡人咸劝。或佽以财。或相以力。经始一两月而工告迄功。殿庑翼然而复桷。黉舍栉然而复芋。丹雘奕然而复章。庖湢复有所。鼎俎复有次。先圣谓子贡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徐侯其有感于此者欤。于是。学之章甫。南涉汕水。访诸平默曰。此不可以无记。吾子其图之。平默以贱陋辞。既不获已。则敬述朱夫子之言而复之曰。崇昔先王。设为学校以教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受学于其中。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之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1H 页
 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及夫学之既成。则又兴其贤者能者而置之列位。是以。当是时也。理义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此先王之学校。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后世学校之设。虽或彷佛乎先王之时。而所谓士学者。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施设之意。则四方之所谓学宫者。止为先圣先师崇德报功之地。而儒冠之出入其中者。其使人皱眉而寒心者。又不可以一二计矣。是以。其效至于风俗日弊。人材日衰。而顾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遂以学校。为虚文冗费。无益有害之设则缪矣。今侯与诸章甫。出谋修葺。实有感于先圣爱礼之意。则自今以始。诚宜思先王施设之意。与夫天赋秉彝。无古今之异。衣冠而入乎黉堂。则相与濯旧图新。励志帅气。讲明圣师之经训。服习圣师之礼教。而凡习俗之用。物欲之诱。不得大为之沴疾。则徐侯之为此。庶几其有辞于方来。而傥圣上一日赫然奋发。富庶吾民。而继之以先王之教。周官司徒之职。明道熙宁之劄。沛然得行于中外。则先是而及此。其功又岂浅浅哉。愿诸君子。以此言。复
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及夫学之既成。则又兴其贤者能者而置之列位。是以。当是时也。理义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焉。此先王之学校。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后世学校之设。虽或彷佛乎先王之时。而所谓士学者。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施设之意。则四方之所谓学宫者。止为先圣先师崇德报功之地。而儒冠之出入其中者。其使人皱眉而寒心者。又不可以一二计矣。是以。其效至于风俗日弊。人材日衰。而顾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遂以学校。为虚文冗费。无益有害之设则缪矣。今侯与诸章甫。出谋修葺。实有感于先圣爱礼之意。则自今以始。诚宜思先王施设之意。与夫天赋秉彝。无古今之异。衣冠而入乎黉堂。则相与濯旧图新。励志帅气。讲明圣师之经训。服习圣师之礼教。而凡习俗之用。物欲之诱。不得大为之沴疾。则徐侯之为此。庶几其有辞于方来。而傥圣上一日赫然奋发。富庶吾民。而继之以先王之教。周官司徒之职。明道熙宁之劄。沛然得行于中外。则先是而及此。其功又岂浅浅哉。愿诸君子。以此言。复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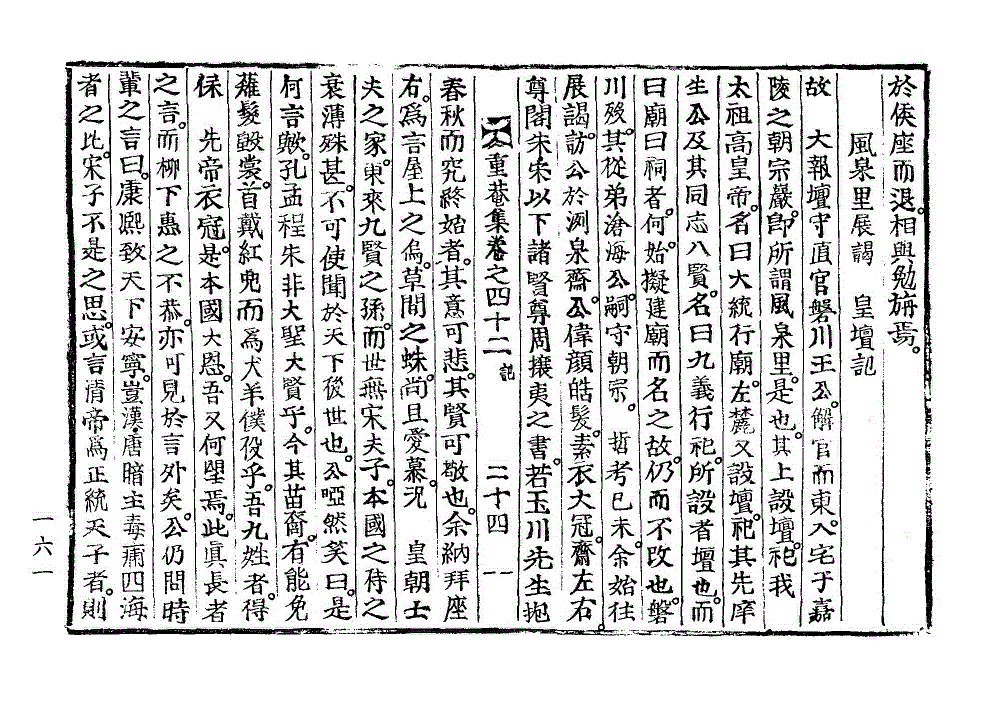 于侯座而退。相与勉旃焉。
于侯座而退。相与勉旃焉。风泉里展谒 皇坛记
故 大报坛守直官磐川王公。解官而东。入宅于嘉陵之朝宗岩。即所谓风泉里。是也。其上设坛。祀我 太祖高皇帝。名曰大统行庙。左麓又设坛。祀其先庠生公及其同志八贤。名曰九义行祀。所设者坛也。而曰庙曰祠者。何。始拟建庙而名之故。仍而不改也。磐川殁。其从弟沧海公。嗣守朝宗。 哲考己未。余始往展谒。访公于洌泉斋。公伟颜皓发。素衣大冠。斋左右。尊阁朱,宋以下诸贤尊周攘夷之书。若玉川先生抱春秋而究终始者。其意可悲。其贤可敬也。余纳拜座右。为言屋上之乌。草间之蛛。尚且爱慕。况 皇朝士夫之家。东来九贤之孙。而世无宋夫子。本国之待之衰薄殊甚。不可使闻于天下后世也。公哑然笑曰。是何言欤。孔孟程朱非大圣大贤乎。今其苗裔。有能免薙发毁裳。首戴红兜而为犬羊仆役乎。吾九姓者。得保 先帝衣冠。是本国大恩。吾又何望焉。此真长者之言。而柳下惠之不恭。亦可见于言外矣。公仍问时辈之言曰。康熙致天下安宁。岂汉,唐暗主毒痡四海者之比。宋子不是之思。或言清帝为正统天子者。则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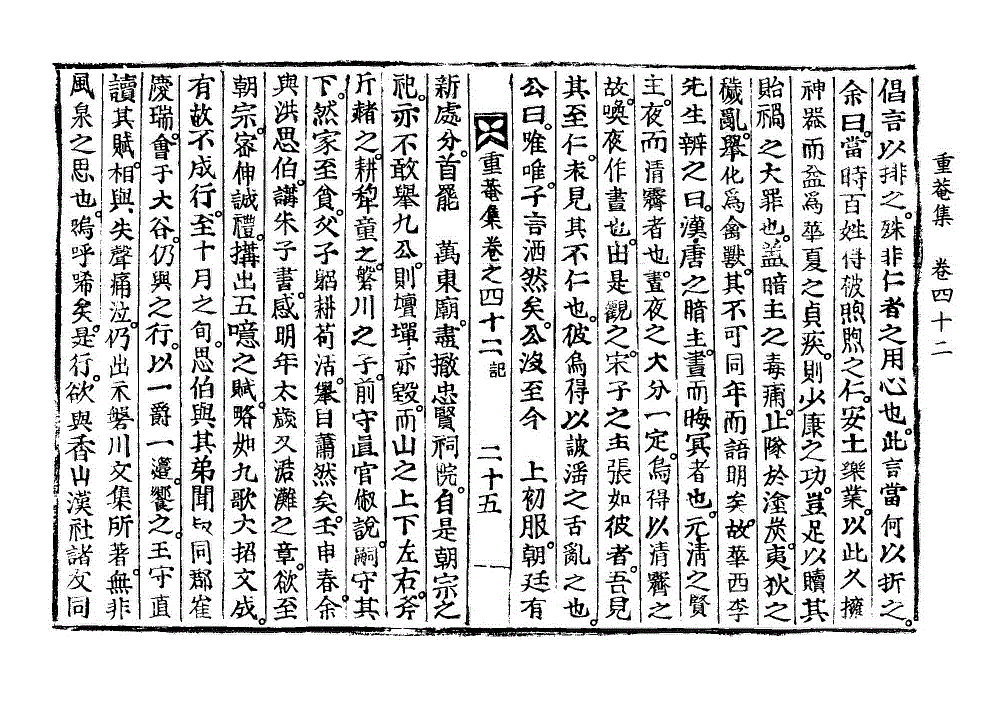 倡言以排之。殊非仁者之用心也。此言当何以折之。余曰。当时百姓得被煦煦之仁。安土乐业。以此久拥神器而益为华夏之贞疾。则少康之功。岂足以赎其贻祸之大罪也。盖暗主之毒痛。止队于涂炭。夷狄之秽乱。举化为禽兽。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故华西李先生辨之曰。汉,唐之暗主。昼而晦冥者也。元,清之贤主。夜而清霁者也。昼夜之大分一定。乌得以清霁之故。唤夜作昼也。由是观之。宋子之主张如彼者。吾见其至仁。未见其不仁也。彼乌得以诐淫之舌乱之也。公曰。唯唯。子言洒然矣。公没至今 上初服。朝廷有新处分。首罢 万东庙。尽撤忠贤祠院。自是朝宗之祀。亦不敢举九公。则坛墠亦毁。而山之上下左右。斧斤赭之。耕犁童之。磐川之子。前守直官俶说。嗣守其下。然家至贫。父子躬耕苟活。举目萧然矣。壬申春。余与洪思伯。讲朱子书。感明年太岁又涒滩之章。欲至朝宗。密伸诚礼。搆出五噫之赋。略如九歌大招文成。有故不成行。至十月之旬。思伯与其弟闻叔同郡崔庆瑞。会于大谷。仍与之行。以一爵一笾。飨之。王守直读其赋。相与失声痛泣。仍出示磐川文集所著。无非风泉之思也。呜呼唏矣。是行。欲与香山汉社诸友同
倡言以排之。殊非仁者之用心也。此言当何以折之。余曰。当时百姓得被煦煦之仁。安土乐业。以此久拥神器而益为华夏之贞疾。则少康之功。岂足以赎其贻祸之大罪也。盖暗主之毒痛。止队于涂炭。夷狄之秽乱。举化为禽兽。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故华西李先生辨之曰。汉,唐之暗主。昼而晦冥者也。元,清之贤主。夜而清霁者也。昼夜之大分一定。乌得以清霁之故。唤夜作昼也。由是观之。宋子之主张如彼者。吾见其至仁。未见其不仁也。彼乌得以诐淫之舌乱之也。公曰。唯唯。子言洒然矣。公没至今 上初服。朝廷有新处分。首罢 万东庙。尽撤忠贤祠院。自是朝宗之祀。亦不敢举九公。则坛墠亦毁。而山之上下左右。斧斤赭之。耕犁童之。磐川之子。前守直官俶说。嗣守其下。然家至贫。父子躬耕苟活。举目萧然矣。壬申春。余与洪思伯。讲朱子书。感明年太岁又涒滩之章。欲至朝宗。密伸诚礼。搆出五噫之赋。略如九歌大招文成。有故不成行。至十月之旬。思伯与其弟闻叔同郡崔庆瑞。会于大谷。仍与之行。以一爵一笾。飨之。王守直读其赋。相与失声痛泣。仍出示磐川文集所著。无非风泉之思也。呜呼唏矣。是行。欲与香山汉社诸友同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2L 页
 之。恐人众而烦于听闻故不果。又记华西先生。欲建茆亭于岩傍。掣肘未就。柳友稚程。恨之。蚤晚欲成其遗志。要吾辈相地。预名见心。盖取复卦彖传之文也。是月之望。遗民金平默。抆涕而记。
之。恐人众而烦于听闻故不果。又记华西先生。欲建茆亭于岩傍。掣肘未就。柳友稚程。恨之。蚤晚欲成其遗志。要吾辈相地。预名见心。盖取复卦彖传之文也。是月之望。遗民金平默。抆涕而记。信斋记
友人柳景茂上舍。少贫失学。长而过房。则服其先大父甫山公。身教所以开发良知者。盖有以异于常人矣。余自北山时。过蒙亲厚。十数年如一日。其宗弟处士稚程。学问德义。菀然为儒林高蹈。则爱好而无斁。有如同堂之亲矣。是岁。余与稚程。先后渡汕水。寓于嘉陵之山。而景茂实为之主。既又与其族父荷塘居士景彦。身率子弟后生。周旋于观善讲习之间。又有以耸动一时之耳目矣。一日以信斋名其室。揖余而进之曰。愿有说焉。余辞谢不获。则因窃取程朱之意。而复之曰信之为言实也。人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其得夫仁义礼智之全。而所谓仁义礼智之全者。又皆至实而无一毫之虚伪也。故信之一言。与仁义礼智。列为五性之目。而人之五性。在天即五行之德也。土之于水火金木。无所不在。故信之于仁义礼智。无所不贯。是故。君子于心术。曰用之间。自一身之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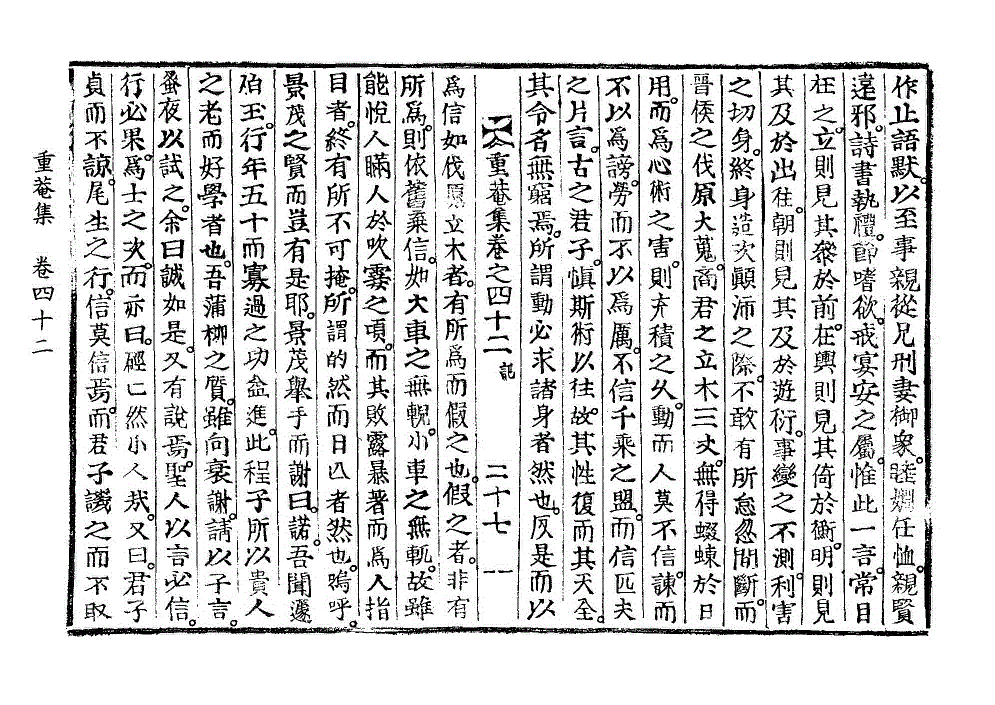 作止语默。以至事亲从兄刑妻御众。睦姻任恤。亲贤远邪。诗书执礼。节嗜欲。戒宴安之属。惟此一言。常目在之。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明则见其及于出往。朝则见其及于游衍。事变之不测。利害之切身。终身造次颠沛之际。不敢有所怠忽间断。而晋侯之伐原大蒐。商君之立木三丈。无得螮蝀于日用。而为心术之害。则充积之久。动而人莫不信。谏而不以为谤。劳而不以为厉。不信千乘之盟。而信匹夫之片言。古之君子。慎斯术以往。故其性复而其天全。其令名无穷焉。所谓动必求诸身者然也。反是而以为信如伐原立木者。有所为而假之也。假之者。非有所为。则依旧弃信。如大车之无輗。小车之无軏。故虽能悦人瞒人于吹霎之顷。而其败露暴著而为人指目者。终有所不可掩。所谓的然而日亡者然也。呜呼。景茂之贤而岂有是耶。景茂举手而谢曰。诺。吾闻蘧伯玉。行年五十而寡过之功益进。此程子所以贵人之老而好学者也。吾蒲柳之质。虽向衰谢。请以子言。蚤夜以试之。余曰诚如是。又有说焉。圣人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士之次。而亦曰。硁硁然小人哉。又曰。君子贞而不谅。尾生之行。信莫信焉。而君子讥之而不取
作止语默。以至事亲从兄刑妻御众。睦姻任恤。亲贤远邪。诗书执礼。节嗜欲。戒宴安之属。惟此一言。常目在之。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明则见其及于出往。朝则见其及于游衍。事变之不测。利害之切身。终身造次颠沛之际。不敢有所怠忽间断。而晋侯之伐原大蒐。商君之立木三丈。无得螮蝀于日用。而为心术之害。则充积之久。动而人莫不信。谏而不以为谤。劳而不以为厉。不信千乘之盟。而信匹夫之片言。古之君子。慎斯术以往。故其性复而其天全。其令名无穷焉。所谓动必求诸身者然也。反是而以为信如伐原立木者。有所为而假之也。假之者。非有所为。则依旧弃信。如大车之无輗。小车之无軏。故虽能悦人瞒人于吹霎之顷。而其败露暴著而为人指目者。终有所不可掩。所谓的然而日亡者然也。呜呼。景茂之贤而岂有是耶。景茂举手而谢曰。诺。吾闻蘧伯玉。行年五十而寡过之功益进。此程子所以贵人之老而好学者也。吾蒲柳之质。虽向衰谢。请以子言。蚤夜以试之。余曰诚如是。又有说焉。圣人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士之次。而亦曰。硁硁然小人哉。又曰。君子贞而不谅。尾生之行。信莫信焉。而君子讥之而不取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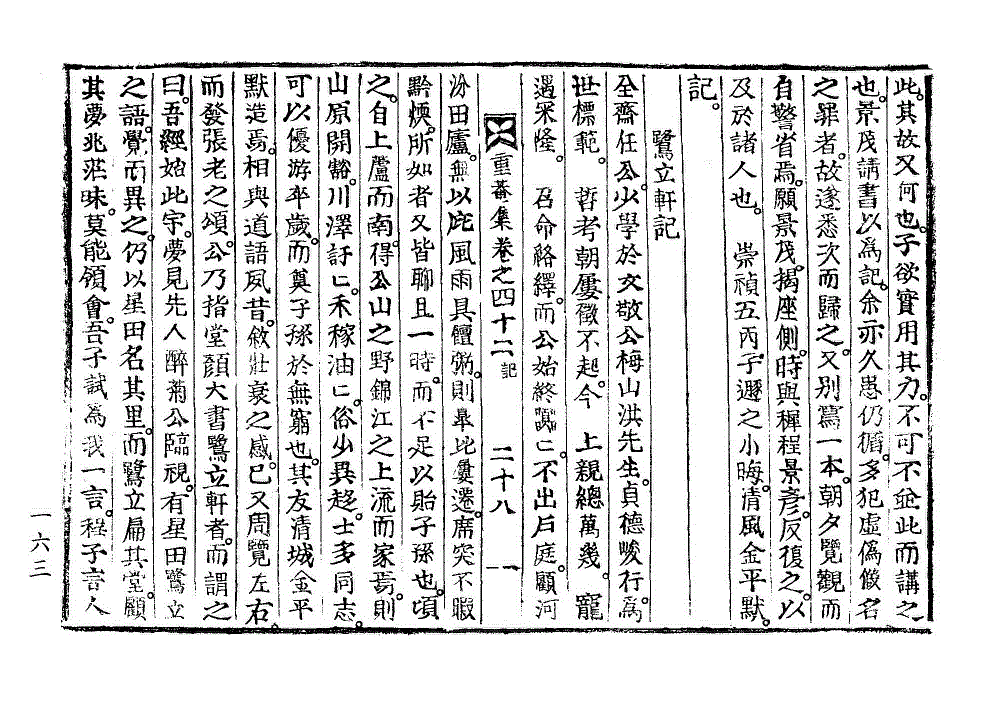 此。其故又何也。子欲实用其力。不可不并此而讲之也。景茂请书以为记。余亦久患仍循。多犯虚伪假名之罪者。故遂悉次而归之。又别写一本。朝夕览观而自警省焉。愿景茂。揭座侧。时与稚程景彦。反复之。以及于诸人也。 崇祯五丙子遁之小晦。清风金平默。记。
此。其故又何也。子欲实用其力。不可不并此而讲之也。景茂请书以为记。余亦久患仍循。多犯虚伪假名之罪者。故遂悉次而归之。又别写一本。朝夕览观而自警省焉。愿景茂。揭座侧。时与稚程景彦。反复之。以及于诸人也。 崇祯五丙子遁之小晦。清风金平默。记。鹭立轩记
全斋任公。少学于文敬公梅山洪先生。贞德峻行。为世标范。 哲考朝屡徵不起。今 上亲总万几。 宠遇深隆。 召命络绎。而公始终嚣嚣。不出户庭。顾河汾田庐。无以庇风雨具饘粥。则皋比屡迁。席突不暇黔暖。所如者又皆聊且一时。而不足以贻子孙也。顷之。自上芦而南。得公山之野锦江之上流而家焉。则山原开豁。川泽吁吁。禾稼油油。俗少异趍。士多同志。可以优游卒岁。而奠子孙于无穷也。其友清城金平默造焉。相与道语夙昔。叙壮衰之感。已又周览左右。而发张老之颂。公乃指堂颜大书鹭立轩者。而谓之曰。吾经始此宇。梦见先人醉菊公临视。有星田鹭立之语。觉而异之。仍以星田名其里。而鹭立扁其堂。顾其梦兆茫昧。莫能领会。吾子试为我一言。程子言人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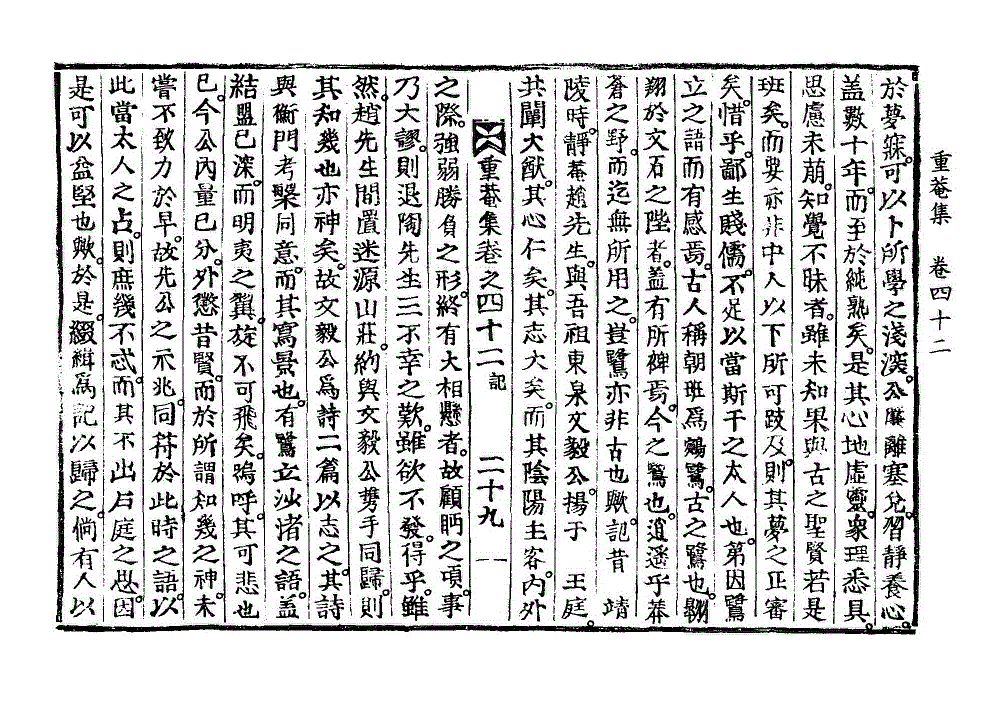 于梦寐。可以卜所学之浅深。公攘离塞兑。习静养心。盖数十年。而至于纯熟矣。是其心地虚灵。众理悉具。思虑未萌。知觉不昧者。虽未知果与古之圣贤若是班矣。而要亦非中人以下所可跂及。则其梦之正审矣。惜乎。鄙生贱儒。不足以当斯干之太人也。第因鹭立之语而有感焉。古人称朝班为鹓鹭。古之鹭也。翱翔于文石之陛者。盖有所裨焉。今之鹭也。逍遥乎莽苍之野。而迄无所用之。岂鹭亦非古也欤。记昔 靖陵时。静庵赵先生。与吾祖东泉文毅公。扬于 王庭。共阐大猷。其心仁矣。其志大矣。而其阴阳主客。内外之际。强弱胜负之形。终有大相悬者。故顾眄之顷。事乃大谬。则退陶先生三不幸之叹。虽欲不发。得乎。虽然。赵先生间置迷源山庄。约与文毅公携手同归。则其知几也亦神矣。故文毅公为诗二篇以志之。其诗与衡门考槃同意。而其写景也。有鹭立沙渚之语。盖结盟已深。而明夷之翼。旋不可飞矣。呜呼。其可悲也已。今公内量己分。外惩昔贤。而于所谓知几之神。未尝不致力于早。故先公之示兆。同符于此时之语。以此当太人之占。则庶几不忒。而其不出户庭之思。因是可以益坚也欤。于是。缀缉为记以归之。倘有人以
于梦寐。可以卜所学之浅深。公攘离塞兑。习静养心。盖数十年。而至于纯熟矣。是其心地虚灵。众理悉具。思虑未萌。知觉不昧者。虽未知果与古之圣贤若是班矣。而要亦非中人以下所可跂及。则其梦之正审矣。惜乎。鄙生贱儒。不足以当斯干之太人也。第因鹭立之语而有感焉。古人称朝班为鹓鹭。古之鹭也。翱翔于文石之陛者。盖有所裨焉。今之鹭也。逍遥乎莽苍之野。而迄无所用之。岂鹭亦非古也欤。记昔 靖陵时。静庵赵先生。与吾祖东泉文毅公。扬于 王庭。共阐大猷。其心仁矣。其志大矣。而其阴阳主客。内外之际。强弱胜负之形。终有大相悬者。故顾眄之顷。事乃大谬。则退陶先生三不幸之叹。虽欲不发。得乎。虽然。赵先生间置迷源山庄。约与文毅公携手同归。则其知几也亦神矣。故文毅公为诗二篇以志之。其诗与衡门考槃同意。而其写景也。有鹭立沙渚之语。盖结盟已深。而明夷之翼。旋不可飞矣。呜呼。其可悲也已。今公内量己分。外惩昔贤。而于所谓知几之神。未尝不致力于早。故先公之示兆。同符于此时之语。以此当太人之占。则庶几不忒。而其不出户庭之思。因是可以益坚也欤。于是。缀缉为记以归之。倘有人以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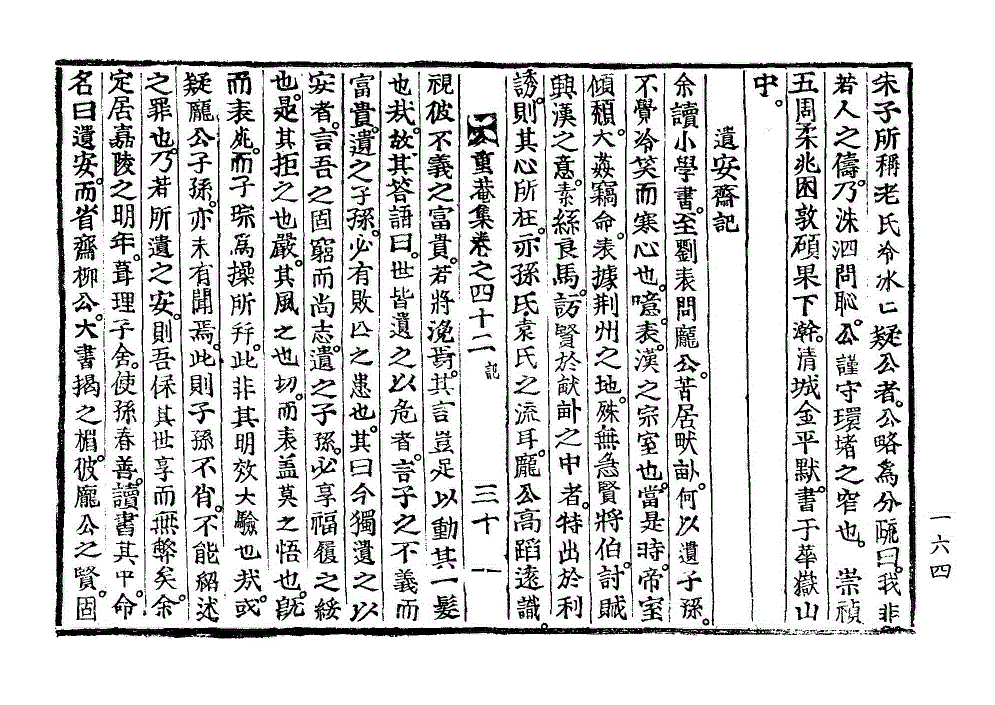 朱子所称老氏冷冰冰疑公者。公略为分疏曰。我非若人之俦。乃洙泗问耻。公谨守环堵之窄也。 崇祯五周柔兆困敦硕果下浣。清城金平默。书于华岳山中。
朱子所称老氏冷冰冰疑公者。公略为分疏曰。我非若人之俦。乃洙泗问耻。公谨守环堵之窄也。 崇祯五周柔兆困敦硕果下浣。清城金平默。书于华岳山中。遗安斋记
余读小学书。至刘表问庞公。苦居畎亩。何以遗子孙。不觉冷笑而寒心也。噫。表。汉之宗室也。当是时。帝室倾颓。大奸窃命。表据荆州之地殊无急贤将伯。讨贼兴汉之意。素丝良马。访贤于𤱶亩之中者。特出于利诱。则其心所在。亦孙氏,袁氏之流耳。庞公高蹈远识。视彼不义之富贵。若将浼焉。其言岂足以动其一发也哉。故其答语曰。世皆遗之以危者。言子之不义而富贵。遗之子孙。必有败亡之患也。其曰今独遗之以安者。言吾之固穷而尚志。遗之子孙。必享福履之绥也。是其拒之也严。其风之也切。而表盖莫之悟也。既而表死。而子琮为操所并。此非其明效大验也哉。或疑庞公子孙。亦未有闻焉。此则子孙不肖。不能绍述之罪也。乃若所遗之安。则吾保其世享而无弊矣。余定居嘉陵之明年。葺理子舍。使孙春善。读书其中。命名曰遗安。而省斋柳公。大书揭之楣。彼庞公之贤。固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5H 页
 非后生所敢跂及。然窃尝诵服周子之训。于所谓道充身安。铢轩冕而尘金玉者。取舍之决。不至为懵然。则其所遗。亦不害为庞公之意也欤。抑庞公之所遗。非溺于畎亩细民之事。如樊须之稼圃。固不待分疏而知之。独其子孙所受。入头下手处。不少槩见焉。今试以伊洛之成法。补之程子承周子道充之绪。而上溯孔颜克己复礼之传。盖尝履绳蹈矩。惟日不足。而进于圣域矣。既老门人问曰。夫子谨于礼四十年。应甚劳苦。程子曰。吾日履安地。何劳苦之有。他人日。履危地。是乃劳苦也。此言当为遗安之实也。然程子之所谨而进于圣域者。乃颜子所复之全体也。惟其为初学言者。则有曰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有曰才放肆则日就旷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朱子编辑小学。以训蒙士。其著家礼。以通礼为冠者。亦皆程子之意。而吃紧为人者也。呜呼。春善乎。汝其寝处此斋。夙夜恐惧。主敬执礼。以为田地。而博文克己。曰惟以相则。异时所造。其高下浅深。吾不可逆料。要之福履之绥。随其所感。其应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呜呼。春善乎。勉之勉之。无得如庞公子孙不肖而无闻也。若然者。老祖不得瞑目于九原也。 崇祯
非后生所敢跂及。然窃尝诵服周子之训。于所谓道充身安。铢轩冕而尘金玉者。取舍之决。不至为懵然。则其所遗。亦不害为庞公之意也欤。抑庞公之所遗。非溺于畎亩细民之事。如樊须之稼圃。固不待分疏而知之。独其子孙所受。入头下手处。不少槩见焉。今试以伊洛之成法。补之程子承周子道充之绪。而上溯孔颜克己复礼之传。盖尝履绳蹈矩。惟日不足。而进于圣域矣。既老门人问曰。夫子谨于礼四十年。应甚劳苦。程子曰。吾日履安地。何劳苦之有。他人日。履危地。是乃劳苦也。此言当为遗安之实也。然程子之所谨而进于圣域者。乃颜子所复之全体也。惟其为初学言者。则有曰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有曰才放肆则日就旷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朱子编辑小学。以训蒙士。其著家礼。以通礼为冠者。亦皆程子之意。而吃紧为人者也。呜呼。春善乎。汝其寝处此斋。夙夜恐惧。主敬执礼。以为田地。而博文克己。曰惟以相则。异时所造。其高下浅深。吾不可逆料。要之福履之绥。随其所感。其应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呜呼。春善乎。勉之勉之。无得如庞公子孙不肖而无闻也。若然者。老祖不得瞑目于九原也。 崇祯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5L 页
 五丁丑孟秋。重庵。书。
五丁丑孟秋。重庵。书。石华斋记
吾道东来。石潭李氏,华阳宋氏。二夫子相继而起。得朱夫子全体大用之传。盖石潭以上知之资。阔步长趍而至。华阳。以大贤之资。临深履薄而至。虽因禀质不同而造德各异。然其为天民之德。王佐之材。则一也。学者于此。不可以辄定优劣。又不可以关西夫子汝南颜子同例。而视为一国之善士也。虽然。石潭之生当 皇明之盛。故事功不及于天下。华阳当天地翻覆之时。身任礼义之大宗。则又与东迁周而孔子生。宋南渡而朱子出。同。当一治之数者也。鼓山任公。少师梅山文敬公。寻二夫子之绪。为世名儒。郑处士君祚父。闻而慕之。诣门请学。任公嘉其志。仍以石华命名其斋。使之朝夕寓慕。而没身钻仰焉。君祚受命不贰。如南轩之学于衡山。而为程氏之纯臣。凡傍人之是非。一己之荣悴。泊然不入于心。呜呼。锦川翁之独复。不佞尝兄事之。今君祚又同其洒落矣。任公殁。君祚以不佞尝师梅山,华西二先生。与任公大体烂漫不相参差。贻书以请记。不佞感其相知之深。有异于馀子。不辞而复之曰。二夫子生于褊邦而能接华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6H 页
 夏道统之传者。子知其所以乎。一言以蔽之。曰为己务实。克己从善而已矣。惟其如是。故真能公听并观也。真能舍己从人也。真能改过不吝也。真能去克伐怨欲也。真能审诐淫邪遁也。真能事事理会。求是而去非也。所谓居敬穷理。存养省察。而践之日用之间者。皆实事而非虚名也。是以。积累之久。欲蜕理融。如光风霁月。如泰山乔岳。民到于今赖之。子欲没身钻仰。其亦勉于此而已矣。若夫藉其该博。衒其文辞。脩其边幅而骋其巧佞。以济其党同伐异。假真售伪之私者。其于二夫子之传授心法。何止百千万里之远也。君祚之贤。不佞保其无此矣。而苋陆之夬夬中。或有未光。则不敢不窃附虞廷戒敖之义。以为记文之乱焉。呜呼。今日何等时也。深目高准之祸。倍蓰于华阳之所值矣。自治之道。岂容造次疏而颠沛忽乎。君祚其亦勉旃。又以加老年之鞭也。
夏道统之传者。子知其所以乎。一言以蔽之。曰为己务实。克己从善而已矣。惟其如是。故真能公听并观也。真能舍己从人也。真能改过不吝也。真能去克伐怨欲也。真能审诐淫邪遁也。真能事事理会。求是而去非也。所谓居敬穷理。存养省察。而践之日用之间者。皆实事而非虚名也。是以。积累之久。欲蜕理融。如光风霁月。如泰山乔岳。民到于今赖之。子欲没身钻仰。其亦勉于此而已矣。若夫藉其该博。衒其文辞。脩其边幅而骋其巧佞。以济其党同伐异。假真售伪之私者。其于二夫子之传授心法。何止百千万里之远也。君祚之贤。不佞保其无此矣。而苋陆之夬夬中。或有未光。则不敢不窃附虞廷戒敖之义。以为记文之乱焉。呜呼。今日何等时也。深目高准之祸。倍蓰于华阳之所值矣。自治之道。岂容造次疏而颠沛忽乎。君祚其亦勉旃。又以加老年之鞭也。听天堂记
我嘉陵太守李侯。莅龟山之侨舍。命平默曰。吾以听天。颜吾堂。烦吾子一言以发之。平默辞谢不获命。盖平默至愚极陋。其于徐孺子之高致。不足以梦攀脚板。而侯到郡之初。遽自枉屈。实用陈仲举故事。视篆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6L 页
 未浃一月。不动声色。弥缝公私之事。扶植礼义之宗。而誊乎一方之口碑者。莫非听天之实也。傥无遽归。夙兴夜寐。推类以尽其馀。则听之之道。即此而在矣。何待言为。无已则有一焉。自诗书以下。至孔孟程朱。动必言天。如曰天君也。天叙也。天秩也。天物也。天位也。天职也。天禄也。如曰天者。理也。如曰天专言之则道也。如曰存心养性以事天也。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也。如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此皆何谓也。岂直谓穹然在上者欤。窃以天也者。天之气也。地也者。天之质也。人也者。天之心也。洪纤高下。飞潜动植。古今事变。充溢于两间也者。天之百骸万形也。合而观之。则天之全体也。其主宰乎是。准则乎是者。则所谓道也理也。故曰昊天曰明。及尔出往。昊天曰朝。及尔游衍。言无一物而非天也。礼义三百。威仪三千。言无一事而非天也。是故。杀一不辜。谓之贼天。行一不义。谓之逆天。一念少差。一事少失。一夫少有向隅与凡折一木。杀一虫。不以其当。皆谓之慢天。此获罪于天之说也。是以。君子无时不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至有八十而受丹书之警者矣。有九十作抑诗之箴者矣。此存心养性。以事天之说也。畏天之威。于时
未浃一月。不动声色。弥缝公私之事。扶植礼义之宗。而誊乎一方之口碑者。莫非听天之实也。傥无遽归。夙兴夜寐。推类以尽其馀。则听之之道。即此而在矣。何待言为。无已则有一焉。自诗书以下。至孔孟程朱。动必言天。如曰天君也。天叙也。天秩也。天物也。天位也。天职也。天禄也。如曰天者。理也。如曰天专言之则道也。如曰存心养性以事天也。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也。如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此皆何谓也。岂直谓穹然在上者欤。窃以天也者。天之气也。地也者。天之质也。人也者。天之心也。洪纤高下。飞潜动植。古今事变。充溢于两间也者。天之百骸万形也。合而观之。则天之全体也。其主宰乎是。准则乎是者。则所谓道也理也。故曰昊天曰明。及尔出往。昊天曰朝。及尔游衍。言无一物而非天也。礼义三百。威仪三千。言无一事而非天也。是故。杀一不辜。谓之贼天。行一不义。谓之逆天。一念少差。一事少失。一夫少有向隅与凡折一木。杀一虫。不以其当。皆谓之慢天。此获罪于天之说也。是以。君子无时不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至有八十而受丹书之警者矣。有九十作抑诗之箴者矣。此存心养性。以事天之说也。畏天之威。于时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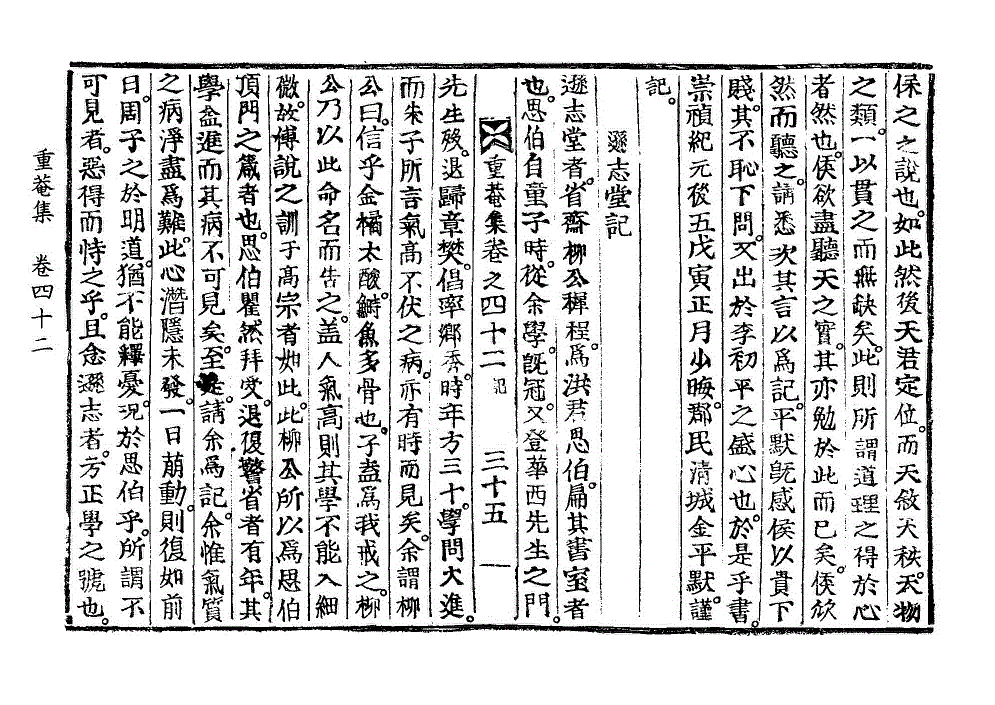 保之之说也。如此然后天君定位。而天叙天秩。天物之类。一以贯之而无缺矣。此则所谓道理之得于心者然也。侯欲尽听天之实。其亦勉于此而已矣。侯欣然而听之。请悉次其言以为记。平默既感侯以贵下贱。其不耻下问。又出于李初平之盛心也。于是乎书。崇祯纪元后五戊寅正月少晦。郡民清城金平默。谨记。
保之之说也。如此然后天君定位。而天叙天秩。天物之类。一以贯之而无缺矣。此则所谓道理之得于心者然也。侯欲尽听天之实。其亦勉于此而已矣。侯欣然而听之。请悉次其言以为记。平默既感侯以贵下贱。其不耻下问。又出于李初平之盛心也。于是乎书。崇祯纪元后五戊寅正月少晦。郡民清城金平默。谨记。逊志堂记
逊志堂者。省斋柳公稚程。为洪君思伯。扁其书室者也。思伯自童子时。从余学。既冠。又登华西先生之门。先生殁。退归章樊。倡率乡秀。时年方三十。学问大进。而朱子所言气高不伏之病。亦有时而见矣。余谓柳公曰。信乎金橘太酸。鲥鱼多骨也。子盍为我戒之。柳公乃以此命名而告之。盖人气高则其学不能入细微。故傅说之训于高宗者如此。此柳公所以为思伯顶门之箴者也。思伯瞿然拜受。退复警省者有年。其学益进而其病不可见矣。至是。请余为记。余惟气质之病净尽为难。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则复如前日。周子之于明道。犹不能释忧。况于思伯乎。所谓不可见者。恶得而恃之乎。且念逊志者。方正学之号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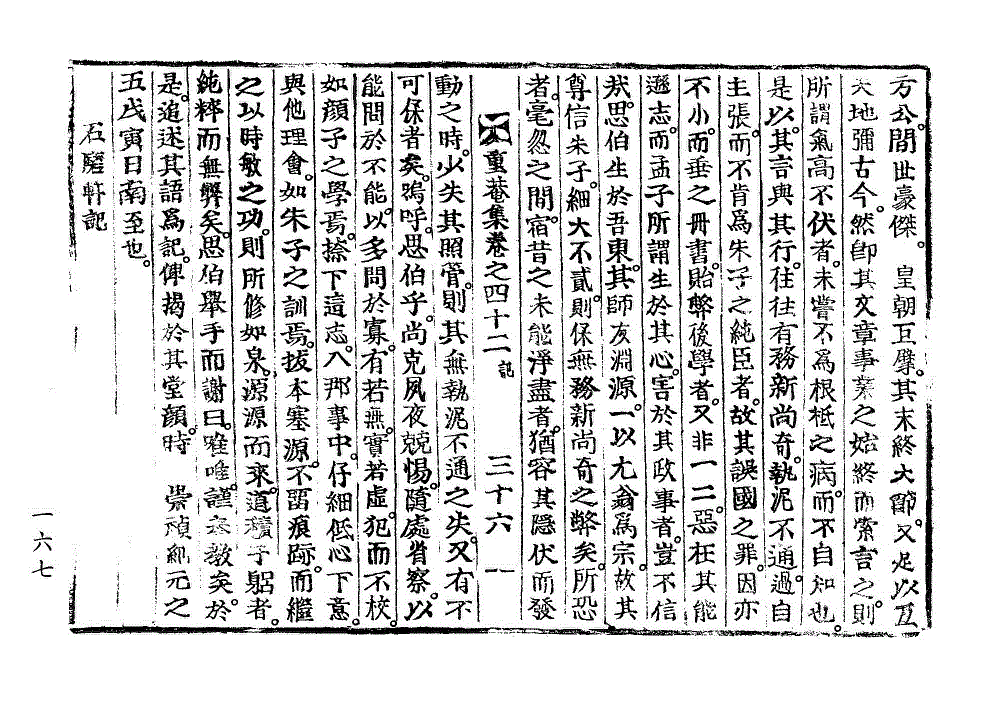 方公。间世豪杰。 皇朝巨擘。其末终大节。又足以亘天地弥古今。然即其文章事业之始终而索言之。则所谓气高不伏者。未尝不为根柢之病。而不自知也。是以。其言与其行。往往有务新尚奇。执泥不通。过自主张。而不肯为朱子之纯臣者。故其误国之罪。因亦不小。而垂之册书。贻弊后学者。又非一二。恶在其能逊志。而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事者。岂不信哉。思伯生于吾东。其师友渊源。一以尤翁为宗。故其尊信朱子。细大不贰。则保无务新尚奇之弊矣。所恐者。毫忽之间。宿昔之未能净尽者。犹容其隐伏而发动之时。少失其照管。则其无执泥不通之失。又有不可保者矣。呜呼。思伯乎。尚克夙夜兢惕。随处省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如颜子之学焉。捺下这志。入那事中。仔细低心下意。与他理会。如朱子之训焉。拔本塞源。不留痕迹。而继之以时敏之功。则所修如泉。源源而来。道积于躬者。纯粹而无弊矣。思伯举手而谢曰。唯唯。谨奉教矣。于是。追述其语为记。俾揭于其堂颜。时 崇祯纪元之五戊寅日南至也。
方公。间世豪杰。 皇朝巨擘。其末终大节。又足以亘天地弥古今。然即其文章事业之始终而索言之。则所谓气高不伏者。未尝不为根柢之病。而不自知也。是以。其言与其行。往往有务新尚奇。执泥不通。过自主张。而不肯为朱子之纯臣者。故其误国之罪。因亦不小。而垂之册书。贻弊后学者。又非一二。恶在其能逊志。而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事者。岂不信哉。思伯生于吾东。其师友渊源。一以尤翁为宗。故其尊信朱子。细大不贰。则保无务新尚奇之弊矣。所恐者。毫忽之间。宿昔之未能净尽者。犹容其隐伏而发动之时。少失其照管。则其无执泥不通之失。又有不可保者矣。呜呼。思伯乎。尚克夙夜兢惕。随处省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如颜子之学焉。捺下这志。入那事中。仔细低心下意。与他理会。如朱子之训焉。拔本塞源。不留痕迹。而继之以时敏之功。则所修如泉。源源而来。道积于躬者。纯粹而无弊矣。思伯举手而谢曰。唯唯。谨奉教矣。于是。追述其语为记。俾揭于其堂颜。时 崇祯纪元之五戊寅日南至也。石磨轩记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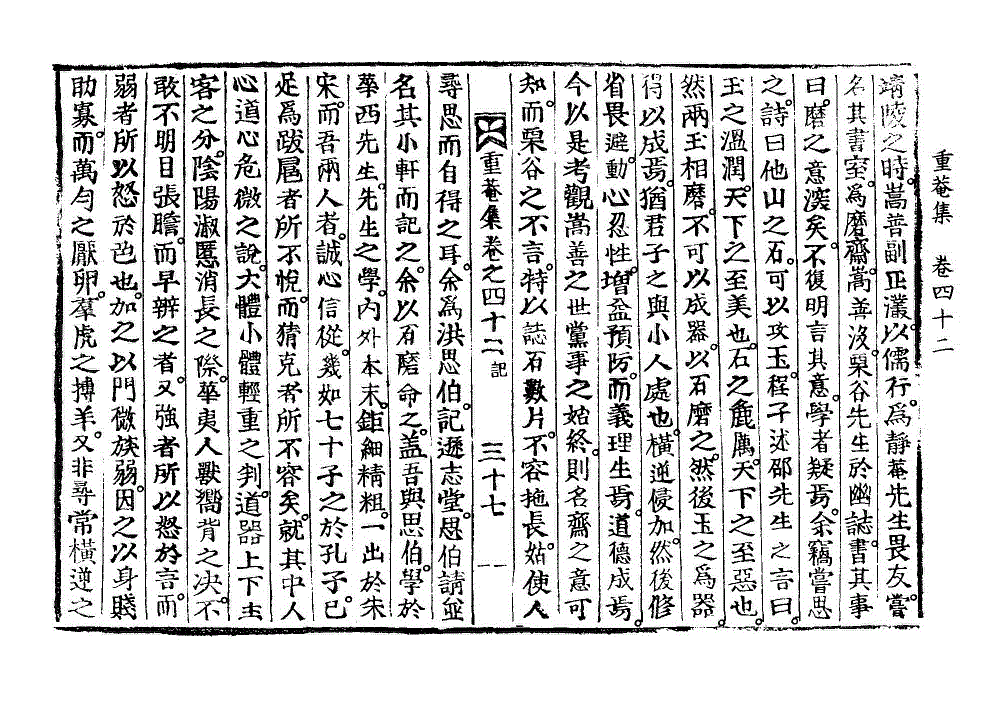 靖陵之时。嵩善副正灇。以儒行。为静庵先生畏友。尝名其书室。为磨斋。嵩善没。栗谷先生于幽志。书其事曰。磨之意深矣。不复明言其意。学者疑焉。余窃尝思之。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子述邵先生之言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今以是考观嵩善之世党事之始终。则名斋之意可知。而栗谷之不言。特以志石数片。不容拖长。姑使人寻思而自得之耳。余为洪思伯。记逊志堂。思伯请并名其小轩而记之。余以石磨命之。盖吾与思伯。学于华西先生。先生之学。内外本末。钜细精粗。一出于朱宋。而吾两人者。诚心信从。几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已足为跋扈者所不悦。而猜克者所不容矣。就其中人心道心危微之说。大体小体轻重之判。道器上下主客之分。阴阳淑慝消长之际。华夷人兽向背之决。不敢不明目张瞻。而早辨之者。又强者所以怒于言。而弱者所以怒于色也。加之以门微族弱。因之以身贱助寡。而万匀之厌卵。群虎之搏羊。又非寻常横逆之
靖陵之时。嵩善副正灇。以儒行。为静庵先生畏友。尝名其书室。为磨斋。嵩善没。栗谷先生于幽志。书其事曰。磨之意深矣。不复明言其意。学者疑焉。余窃尝思之。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子述邵先生之言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今以是考观嵩善之世党事之始终。则名斋之意可知。而栗谷之不言。特以志石数片。不容拖长。姑使人寻思而自得之耳。余为洪思伯。记逊志堂。思伯请并名其小轩而记之。余以石磨命之。盖吾与思伯。学于华西先生。先生之学。内外本末。钜细精粗。一出于朱宋。而吾两人者。诚心信从。几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已足为跋扈者所不悦。而猜克者所不容矣。就其中人心道心危微之说。大体小体轻重之判。道器上下主客之分。阴阳淑慝消长之际。华夷人兽向背之决。不敢不明目张瞻。而早辨之者。又强者所以怒于言。而弱者所以怒于色也。加之以门微族弱。因之以身贱助寡。而万匀之厌卵。群虎之搏羊。又非寻常横逆之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第 168L 页
 比也。于斯时也。若所谓修省畏避。若所谓动心忍性。若所谓增益预防者。岂但如嵩善之时哉。此今日所以命名之意也。呜呼。思伯乎。帝降之衷。不可负。父母之体。不可辱。圣贤之言。不可侮。亲炙之师。不可背。老氏之守玄。不可师。杨氏之为我。不可学。乡愿之媚世。不可法。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又圣人之所大戒也。二者将安所取衷哉。岂不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乎。呜呼。将恐将惧。维予与女。盍相与勉之。既以是告思伯。仍悉次以为记。愿思伯慎密。毋得以揭楣也。恐山禽亦饶舌也。 崇祯五回著雍摄提格见心节。重庵老夫。
比也。于斯时也。若所谓修省畏避。若所谓动心忍性。若所谓增益预防者。岂但如嵩善之时哉。此今日所以命名之意也。呜呼。思伯乎。帝降之衷。不可负。父母之体。不可辱。圣贤之言。不可侮。亲炙之师。不可背。老氏之守玄。不可师。杨氏之为我。不可学。乡愿之媚世。不可法。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又圣人之所大戒也。二者将安所取衷哉。岂不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乎。呜呼。将恐将惧。维予与女。盍相与勉之。既以是告思伯。仍悉次以为记。愿思伯慎密。毋得以揭楣也。恐山禽亦饶舌也。 崇祯五回著雍摄提格见心节。重庵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