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x 页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杂著
杂著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5H 页
 学统考○正统
学统考○正统按朱子于论孟序说。专取史记世家列传之文。此为简当。今于孔孟及仲尼弟子。杂取诸书序次。则真赝不无相蒙者。恐非谨严之道。且在二千年之后。岁月先后无端的可据者。亦以己意强排。殊觉未安。
周子。○顾泾阳曰。程伯子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止)所乐何事。又曰。自再见周茂叔后。(止)吾与点也之意。又有诗曰。云淡风轻近午天。(止)将谓偷閒学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尽元公也。程叔子状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时。(止)反求诸六经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尽元公。且未能尽伯子也。
伯子三条语。何以见其未能尽元公也。上二条。非状德上称停语。下一条。云淡风轻诗。初不干元公事。以此为伯子未能尽元公之證。殊不可晓。至于明道行状。则闻周茂叔论道一句。骤看虽似忽略。然看来道之一字。无所不包。则自孟子没后。论道二字。非茂叔。孰有承当者。未知其要。以下记初年求道时事。而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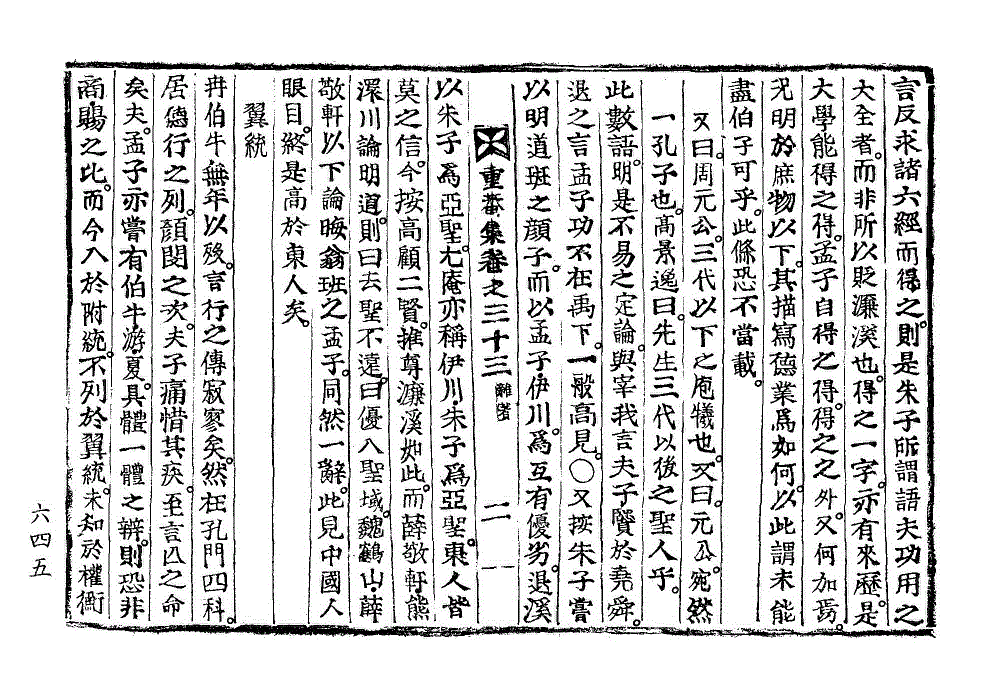 言反求诸六经而得之。则是朱子所谓语夫功用之大全者。而非所以贬濂溪也。得之一字。亦有来历。是大学能得之得。孟子自得之得。得之之外。又何加焉。况明于庶物以下。其描写德业为如何。以此谓未能尽伯子可乎。此条恐不当载。
言反求诸六经而得之。则是朱子所谓语夫功用之大全者。而非所以贬濂溪也。得之一字。亦有来历。是大学能得之得。孟子自得之得。得之之外。又何加焉。况明于庶物以下。其描写德业为如何。以此谓未能尽伯子可乎。此条恐不当载。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牺也。又曰。元公。宛然一孔子也。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后之圣人乎。
此数语。明是不易之定论。与宰我言夫子贤于尧舜。退之言孟子功不在禹下。一般高见。○又按朱子尝以明道斑之颜子。而以孟子,伊川。为互有优劣。退溪以朱子为亚圣。尤庵亦称伊川,朱子为亚圣。东人皆莫之信。今按高顾二贤。推尊濂溪如此。而薛敬轩,熊澴川论明道。则曰去圣不远。曰优入圣域。魏鹤山,薛敬轩以下论晦翁班之孟子。同然一辞。此见中国人眼目。终是高于东人矣。
学统考○翼统
冉伯牛无年以殁。言行之传寂寥矣。然在孔门四科。居德行之列。颜闵之次。夫子痛惜其疾。至言亡之命矣夫。孟子亦尝有伯牛,游,夏。具体一体之辨。则恐非商,赐之比。而今入于附统。不列于翼统。未知于权衡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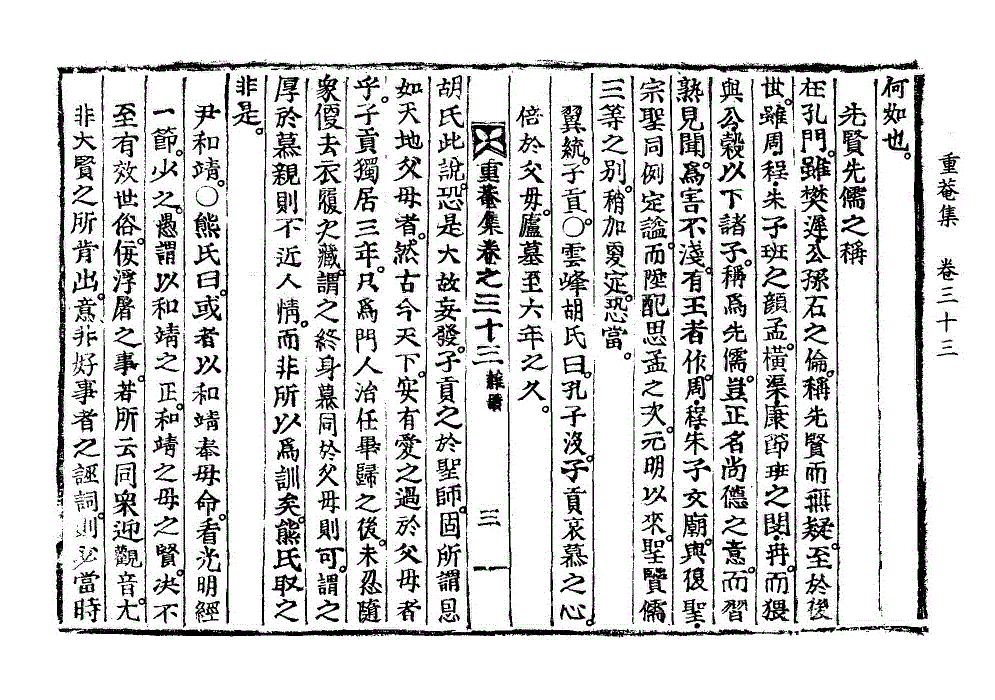 何如也。
何如也。先贤先儒之称
在孔门。虽樊迟,公孙石之伦。称先贤而无疑。至于后世。虽周,程,朱子班之颜孟。横渠,康节班之闵,冉。而猥与公,谷以下诸子。称为先儒。岂正名尚德之意。而习熟见闻。为害不浅。有王者作。周,程,朱子文庙。与复圣,宗圣同例定谥。而升配思孟之次。元明以来。圣贤儒三等之别。稍加更定。恐当。
翼统。子贡。○云峰胡氏曰。孔子没。子贡哀慕之心。倍于父母。庐墓至六年之久。
胡氏此说。恐是大故妄发。子贡之于圣师。固所谓恩如天地父母者。然古今天下。安有爱之过于父母者乎。子贡独居三年。只为门人治任毕归之后。未忍随众便去衣履次藏。谓之终身慕同于父母则可。谓之厚于慕亲则不近人情。而非所以为训矣。熊氏取之非是。
尹和靖。○熊氏曰。或者以和靖奉母命。看光明经一节。少之。愚谓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贤。决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众迎观音。尤非大贤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诬词。则必当时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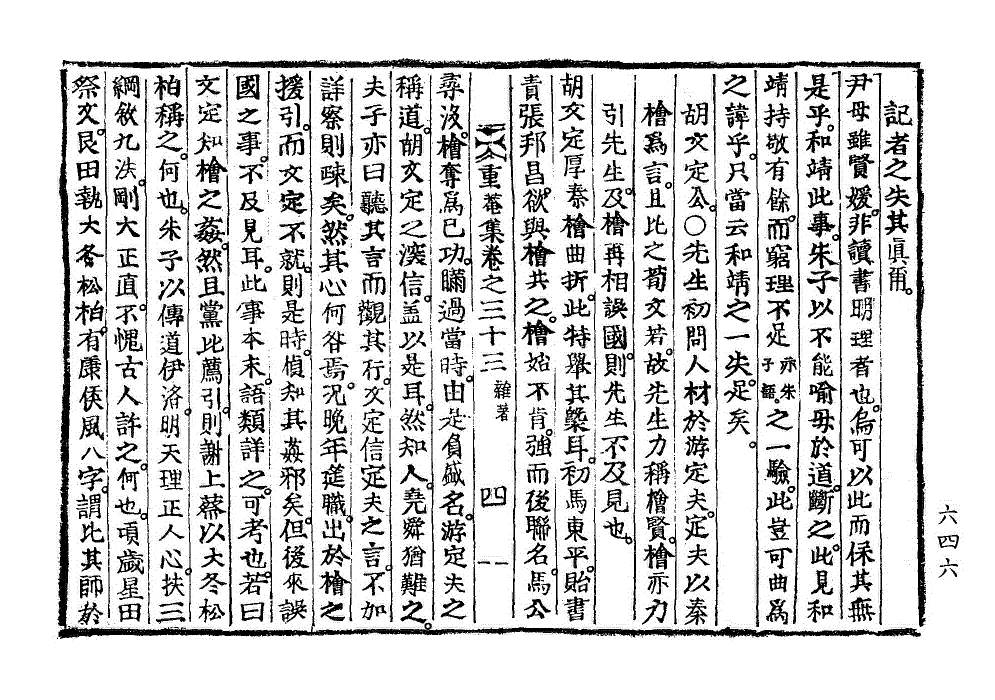 记者之失其真尔。
记者之失其真尔。尹母虽贤媛。非读书明理者也。乌可以此而保其无是乎。和靖此事。朱子以不能喻母于道。断之。此见和靖持敬有馀。而穷理不足(亦朱子语。)之一验。此岂可曲为之讳乎。只当云和靖之一失。足矣。
胡文定公。○先生初问人材于游定夫。定夫以秦桧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称桧贤。桧亦力引先生。及桧再相误国。则先生不及见也。
胡文定厚秦桧曲折。此特举其槩耳。初马东平。贻书责张邦昌。欲与桧共之。桧始不肯。强而后联名。马公寻没。桧夺为己功。瞒过当时。由是负盛名。游定夫之称道。胡文定之深信。盖以是耳。然知人。尧舜犹难之。夫子亦曰听其言而观其行。文定信定夫之言。不加详察则疏矣。然其心何咎焉。况晚年筵职。出于桧之援引。而文定不就。则是时。侦知其奸邪矣。但后来误国之事。不及见耳。此事本未。语类详之。可考也。若曰文定知桧之奸。然且党比荐引。则谢上蔡以大冬松柏称之。何也。朱子以传道伊洛。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刚大正直。不愧古人许之。何也。顷岁星田祭文。艮田执大各松柏。有康侯风八字。谓比其师于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7H 页
 党桧之人。率其同门之人。惹出无限节拍。追思不满一笑。
党桧之人。率其同门之人。惹出无限节拍。追思不满一笑。杨文靖。○熊氏曰。龟山之功。岂在子舆下。
龟山承二程之绪。三传而得朱子。则其功诚不鲜矣。惟熊氏。便欲引而班之孟氏。则直是醉人胡说。不足深辨也。
蔡九峰
九峰之贤。与勉斋列于翼统。吾无间然矣。但九峰之父西山。因数明理。为朱门之高弟。而卓然有功于斯文。晦翁称之为老友。而不敢以门徒视之。这是甚次第而见逸于翼统也。此不能无憾也。因是而有感焉。南宋之末。至无道之世也。如蔡氏四世五贤。名不入于朝籍。至西山九峰。以党祸流落道州。以今入常情言之。从事圣人之道。不获分寸之利。长贪贱而入坎窞如此。是将悔其所学。改其涂辙。而同流合污。以求荣利之不暇。安肯至死不变。而又以世济其美哉。是则蔡氏数贤已矣。以故元史臣脱脱。治宋史。勉斋则有官而显也。列之于道学传。西山九峰。无官而微也。列之于儒林传。始之抑扬物情如此矣。顾眄之顷。公论渐行。则蔡氏父子先祀圣庙之庭。而勉斋反不与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7L 页
 焉。万历间。重峰先生。以书质于礼部。然后最晚得祀。则知百世之定论。初不干于当时之屈伸。皎然矣。世之陷溺良心者。于此亦可省矣。又按此篇末云。次子抗。能世其业者。可发一大笑也。吾不知当时。世其蔡氏之业者。在抗乎。在节斋,觉轩乎。抗也内有父祖之诗礼。外侍考亭之函丈。所讲者何事。当理宗之世。权奸鄙夫坏乱之日。藉其先荫。托其儒名。登高科扬显仕。而至于将相之位。不遭弹谴之辱。安享富贵之荣。非舍其所学。改其涂辙。枉己徇人。浮浮沉沉而求媚于世。其能致此乎。今考续纲目。大书以蔡抗签书枢密院事。而分注但曰元定孙也。无他言行之见。书者书为知枢密参知政事亦然。则其闇然媚世。苟禄尸位之情状。即此可见矣。若是而谓之能世其业。则稍有知识者。谁不失笑也。此说曾于华东史合编发之。今因世业之说而又及之。以示湖南士友云。
焉。万历间。重峰先生。以书质于礼部。然后最晚得祀。则知百世之定论。初不干于当时之屈伸。皎然矣。世之陷溺良心者。于此亦可省矣。又按此篇末云。次子抗。能世其业者。可发一大笑也。吾不知当时。世其蔡氏之业者。在抗乎。在节斋,觉轩乎。抗也内有父祖之诗礼。外侍考亭之函丈。所讲者何事。当理宗之世。权奸鄙夫坏乱之日。藉其先荫。托其儒名。登高科扬显仕。而至于将相之位。不遭弹谴之辱。安享富贵之荣。非舍其所学。改其涂辙。枉己徇人。浮浮沉沉而求媚于世。其能致此乎。今考续纲目。大书以蔡抗签书枢密院事。而分注但曰元定孙也。无他言行之见。书者书为知枢密参知政事亦然。则其闇然媚世。苟禄尸位之情状。即此可见矣。若是而谓之能世其业。则稍有知识者。谁不失笑也。此说曾于华东史合编发之。今因世业之说而又及之。以示湖南士友云。真西山。○熊氏曰。西山德业文章。光明俊伟。所谓斯文正宗。庶几可以无愧也。或以逮事济王一节为恨。夫济王非建成比也。霅川之变。与六月四日之事不相类。后西山入见理宗。惓惓于赠恤。反复乎纲常。亦岂忘情故邸者。呜呼。是亦可以察先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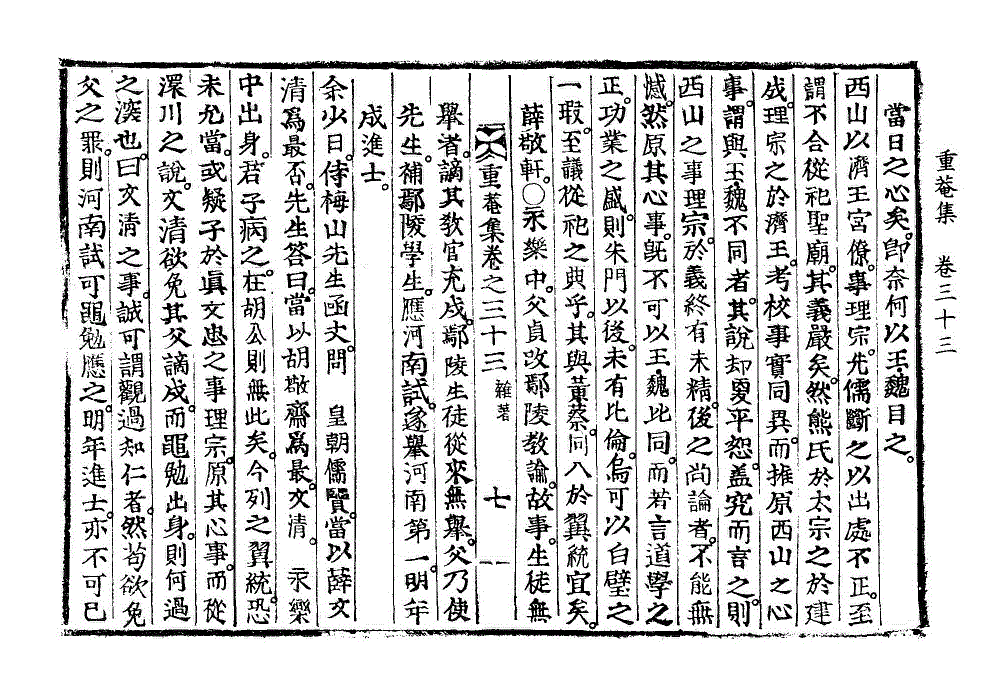 当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
当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西山以济王宫僚。事理宗。先儒断之以出处不正。至谓不合从祀圣庙。其义严矣。然熊氏于太宗之于建成。理宗之于济王。考校事实同异。而推原西山之心事。谓与王,魏不同者。其说却更平恕。盖究而言之。则西山之事理宗。于义终有未精。后之尚论者。不能无憾。然原其心事。既不可以王,魏比同。而若言道学之正。功业之盛。则朱门以后。未有比伦。乌可以白璧之一瑕。至议从祀之典乎。其与黄,蔡。同入于翼统宜矣。
薛敬轩。○永乐中。父贞改鄢陵教谕。故事。生徒无举者。谪其教官充戍。鄢陵生徒从来无举。父乃使先生。补鄢陵学生。应河南试。遂举河南第一。明年成进士。
余少日。侍梅山先生函丈。问 皇朝儒贤。当以薛文清为最否。先生答曰。当以胡敬斋为最。文清。 永乐中出身。君子病之。在胡公则无此矣。今列之翼统。恐未允当。或疑子于真文忠之事理宗。原其心事。而从澴川之说。文清欲免其父谪戍。而黾勉出身。则何过之深也。曰文清之事。诚可谓观过知仁者。然苟欲免父之罪。则河南试可黾勉应之。明年进士。亦不可已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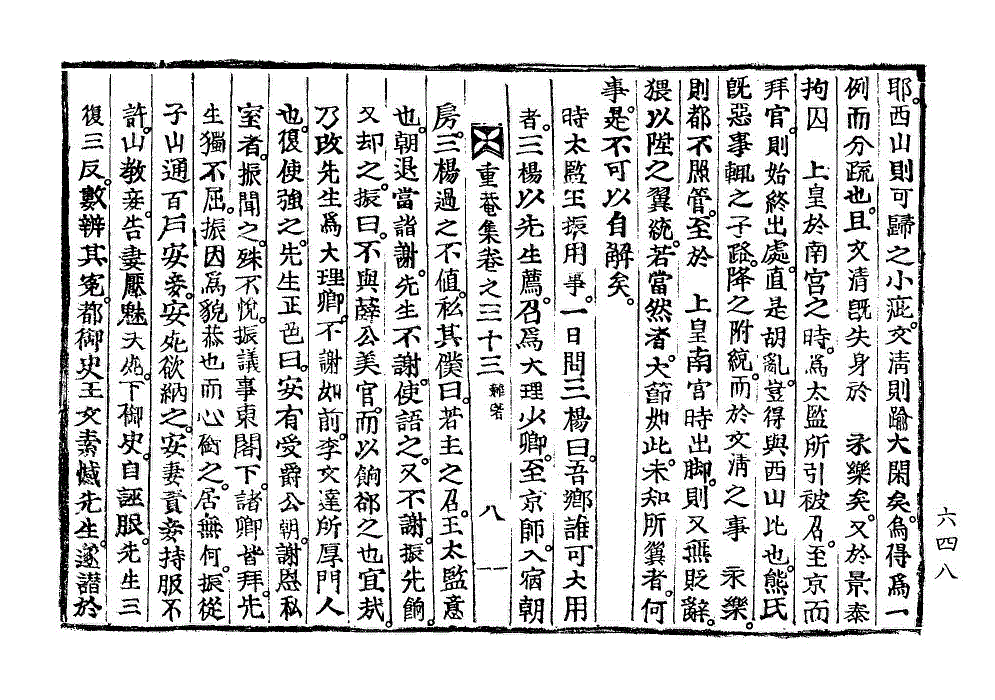 耶。西山则可归之小疵。文清则踰大闲矣。乌得为一例而分疏也。且文清既失身于 永乐矣。又于景泰拘囚 上皇于南宫之时。为太监所引被召。至京而拜官。则始终出处。直是胡乱。岂得与西山比也。熊氏既恶事辄之子路。降之附统。而于文清之事 永乐。则都不照管。至于 上皇南宫时出脚。则又无贬辞。猥以升之翼统。若当然者。大节如此。未知所翼者。何事。是不可以自解矣。
耶。西山则可归之小疵。文清则踰大闲矣。乌得为一例而分疏也。且文清既失身于 永乐矣。又于景泰拘囚 上皇于南宫之时。为太监所引被召。至京而拜官。则始终出处。直是胡乱。岂得与西山比也。熊氏既恶事辄之子路。降之附统。而于文清之事 永乐。则都不照管。至于 上皇南宫时出脚。则又无贬辞。猥以升之翼统。若当然者。大节如此。未知所翼者。何事。是不可以自解矣。时太监王振用事。一日问三杨曰。吾乡谁可大用者。三杨以先生荐。召为大理少卿。至京师。入宿朝房。三杨过之不值。私其仆曰。若主之召。王太监意也。朝退当诣谢。先生不谢。使语之。又不谢。振先饷。又却之。振曰。不与薛公美官。而以饷郤之也宜哉。乃改先生为大理卿。不谢如前。李文达所厚门人也。复使强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者。振闻之。殊不悦。振议事东阁下。诸卿皆拜。先生独不屈。振因为貌恭也而心衔之。居无何。振从子山通百户安妾。安死欲纳之。安妻责妾持服不许。山教妾。告妻压魅夫死。下御史。自诬服。先生三复三反。数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谮于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9H 页
 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贿。出人死罪。有 诏廷问。振曰。是固当死。下锦衣卫狱。手持周易。读诵不辍。至覆奏临刑。神色自若。会振一老仆。泣于爨下。振问何为。仆曰。闻薛夫子贤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将刑。仆是以泣。振问何以知之。仆曰。乡人也。因备言先生生平。振为之动。 诏赦之。放归为民。振死。起为大理寺丞。寻致仕。
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贿。出人死罪。有 诏廷问。振曰。是固当死。下锦衣卫狱。手持周易。读诵不辍。至覆奏临刑。神色自若。会振一老仆。泣于爨下。振问何为。仆曰。闻薛夫子贤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将刑。仆是以泣。振问何以知之。仆曰。乡人也。因备言先生生平。振为之动。 诏赦之。放归为民。振死。起为大理寺丞。寻致仕。按薛公忤王振本末。真可以廉顽立懦也。然在薛公之贤。不得无责备之辞。盖徒知受爵于公朝。谢恩于私室。非君子守身之义。而不知王振用事之朝。非君子出脚之地。可谓知道乎。闵子骞辞费宰曰。如有复我者。吾必在汶上矣谢氏曰。居乱邦见恶人。在圣人则可。自圣人以下。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故闵子早见而预为之所。如此方是知道之验也。薛公既无圣人力量。而王振之时。就召不辞。则其不自量。已甚矣。业已就之。则非随众鹘突而取辱。必独立独忤而取祸。理之所必然也。其视闵子见几勇决。壁立万仞者。何如也。
先生所学。一遵伊,洛微言以为朱某以来。斯道大章。无庸著作。直须躬行尔。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49L 页
 皇明儒者。大率多务新尚奇之病。而敬轩之学。能于程朱笃信如此。则亦贤矣。但谓无庸著作。直须躬行。则语却有病。朱子以后。义理尽备。无一缺漏。固不容叠床架屋。若言自家躬行酬酢万变之道。则学问思辨。须用朱子许多功夫。方始看得朱子出来。自家躬行。触处可以曲当。怎生说直须躬行便休。必如尤翁所言。朱子以后。无一理不明。后学只当尊信朱子。极意讲明。为圣为贤。不外乎此。必欲著书立言者。妄也赘也。如此说。方完备无弊。须知著作。是嘉惠后人之事。是成德后不得已而为之者也。(伊川曰。著书不得已也。)讲明是自家致知之事。以为著作而禁止。则非小失也。
皇明儒者。大率多务新尚奇之病。而敬轩之学。能于程朱笃信如此。则亦贤矣。但谓无庸著作。直须躬行。则语却有病。朱子以后。义理尽备。无一缺漏。固不容叠床架屋。若言自家躬行酬酢万变之道。则学问思辨。须用朱子许多功夫。方始看得朱子出来。自家躬行。触处可以曲当。怎生说直须躬行便休。必如尤翁所言。朱子以后。无一理不明。后学只当尊信朱子。极意讲明。为圣为贤。不外乎此。必欲著书立言者。妄也赘也。如此说。方完备无弊。须知著作。是嘉惠后人之事。是成德后不得已而为之者也。(伊川曰。著书不得已也。)讲明是自家致知之事。以为著作而禁止。则非小失也。整庵罗氏曰。薛文清读书录。有云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当矣。至于反复證明。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愚则不能无疑。夫一有一无。其为缝隙也。大矣。安得谓之器亦道。道亦器耶。盖文清之于理气。亦始终认为二物。故其言未免时有窒碍也。愚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并无窒碍。虽欲寻其缝隙。子不可得矣。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0H 页
 理气。须见其一而二。二而一。惟一也。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惟二也。故孔子曰形而上。形而下。一者。以不离而言也。二者。以不杂而言也。今以此条所论观之。气之聚。有聚之理故也。气之散。有散之理故也。理者。气之主。气者。理之器。理无迹而气有迹。理则通而气则局。故气有聚散。而理则一贯。(以气言则聚非散散非聚。以理言则聚之理即散之理。散之理即聚之理。)无聚散之迹。于此见一而二。二而一之妙也。然其实二物也。(朱子曰。理气决是二物。)薛氏之言。本无可疑。罗氏非之。何也。若曰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以是槩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则是理气一物。更无分别。从古圣贤。既设气之名。又设理之名。何为其不惮烦也。其故可知。以天道言之。春则温而生。夏则暑而长。秋则凉而成。冬则寒而藏。善则降之祥。不善则降之殃。此理之本然而气之循理者也。至或温凉寒暑失其序。殃庆灾祥易其施。则分明是气不循理而理不自做者也。以人道言之。此心寂然不动。而大本无偏倚。感而遂通而七情皆中节。粹然至善。动静一致者。此理之本然而气之循理者也。中体有所偏倚。发用有不中节。七颠八倒。失其本然者。分明是气不循理而理不自做者也。今罗
理气。须见其一而二。二而一。惟一也。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惟二也。故孔子曰形而上。形而下。一者。以不离而言也。二者。以不杂而言也。今以此条所论观之。气之聚。有聚之理故也。气之散。有散之理故也。理者。气之主。气者。理之器。理无迹而气有迹。理则通而气则局。故气有聚散。而理则一贯。(以气言则聚非散散非聚。以理言则聚之理即散之理。散之理即聚之理。)无聚散之迹。于此见一而二。二而一之妙也。然其实二物也。(朱子曰。理气决是二物。)薛氏之言。本无可疑。罗氏非之。何也。若曰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以是槩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则是理气一物。更无分别。从古圣贤。既设气之名。又设理之名。何为其不惮烦也。其故可知。以天道言之。春则温而生。夏则暑而长。秋则凉而成。冬则寒而藏。善则降之祥。不善则降之殃。此理之本然而气之循理者也。至或温凉寒暑失其序。殃庆灾祥易其施。则分明是气不循理而理不自做者也。以人道言之。此心寂然不动。而大本无偏倚。感而遂通而七情皆中节。粹然至善。动静一致者。此理之本然而气之循理者也。中体有所偏倚。发用有不中节。七颠八倒。失其本然者。分明是气不循理而理不自做者也。今罗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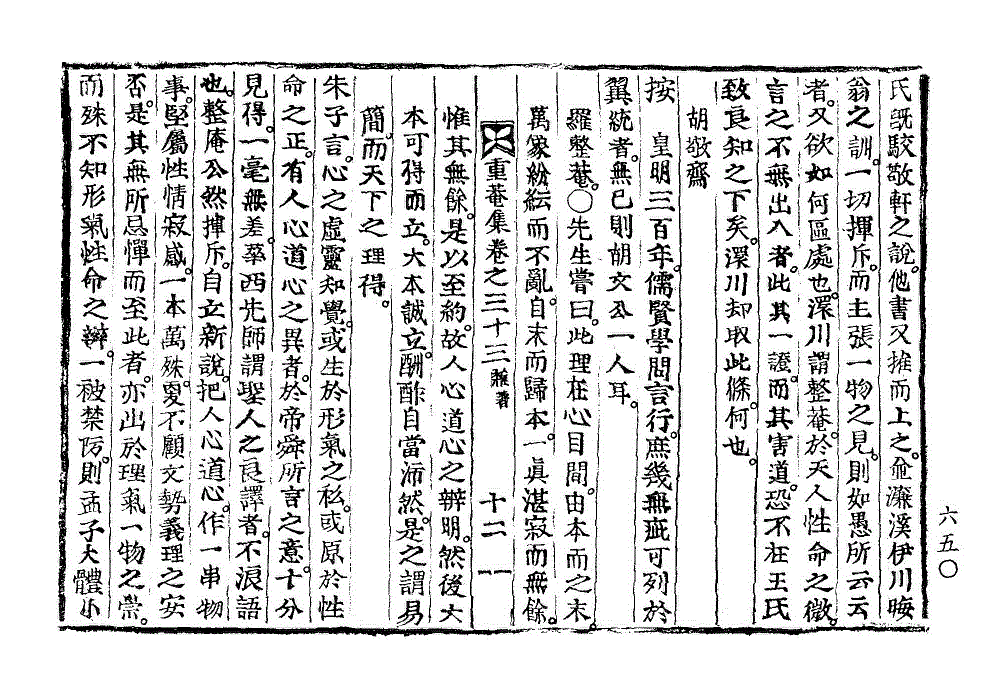 氏既駮敬轩之说。他书又推而上之。并濂溪伊川晦翁之训。一切挥斥。而主张一物之见。则如愚所云云者。又欲如何区处也。澴川谓整庵。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不无出入者。此其一證。而其害道。恐不在王氏致良知之下矣。澴川却取此条。何也。
氏既駮敬轩之说。他书又推而上之。并濂溪伊川晦翁之训。一切挥斥。而主张一物之见。则如愚所云云者。又欲如何区处也。澴川谓整庵。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不无出入者。此其一證。而其害道。恐不在王氏致良知之下矣。澴川却取此条。何也。胡敬斋
按 皇明三百年。儒贤学问言行。庶几无疵可列于翼统者。无已则胡文公一人耳。
罗整庵。○先生尝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惟其无馀。是以至约。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后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诚立。酬酢自当沛然。是之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朱子言。心之虚灵知觉。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于帝舜所言之意。十分见得。一毫无差。华西先师谓圣人之良译者。不浪语也。整庵公然挥斥。自立新说。把人心道心。作一串物事。坚属性情寂感。一本万殊。更不顾文势义理之安否。是其无所忌惮而至此者。亦出于理气一物之崇。而殊不知形气性命之辨。一被禁防。则孟子大体小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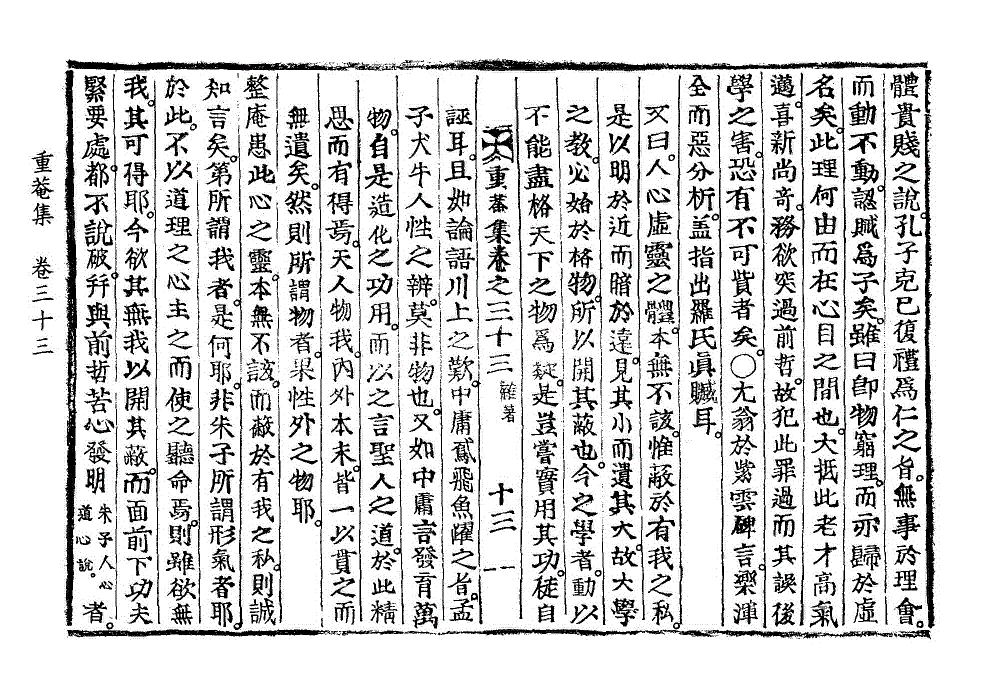 体贵贱之说。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旨。无事于理会。而动不动。认贼为子矣。虽曰即物穷理。而亦归于虚名矣。此理何由而在心目之间也。大抵此老才高气迈。喜新尚奇。务欲突过前哲。故犯此罪过而其误后学之害。恐有不可赀者矣。○尤翁于紫云碑言。乐浑全而恶分析。盖指出罗氏真赃耳。
体贵贱之说。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旨。无事于理会。而动不动。认贼为子矣。虽曰即物穷理。而亦归于虚名矣。此理何由而在心目之间也。大抵此老才高气迈。喜新尚奇。务欲突过前哲。故犯此罪过而其误后学之害。恐有不可赀者矣。○尤翁于紫云碑言。乐浑全而恶分析。盖指出罗氏真赃耳。又曰。人心虚灵之体。本无不该。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远。见其小而遗其大。故大学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开其蔽也。今之学者。动以不能尽格天下之物为疑。是岂尝实用其功。徒自诬耳。且如论语川上之叹。中庸鸢飞鱼跃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圣人之道。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内外本末。皆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然则所谓物者。果性外之物耶。
整庵患此心之灵。本无不该。而蔽于有我之私。则诚知言矣。第所谓我者。是何耶。非朱子所谓形气者耶。于此。不以道理之心主之而使之听命焉。则虽欲无我。其可得耶。今欲其无我以开其蔽。而面前下功夫紧要处。都不说破。并与前哲苦心发明(朱子人心道心说。)者。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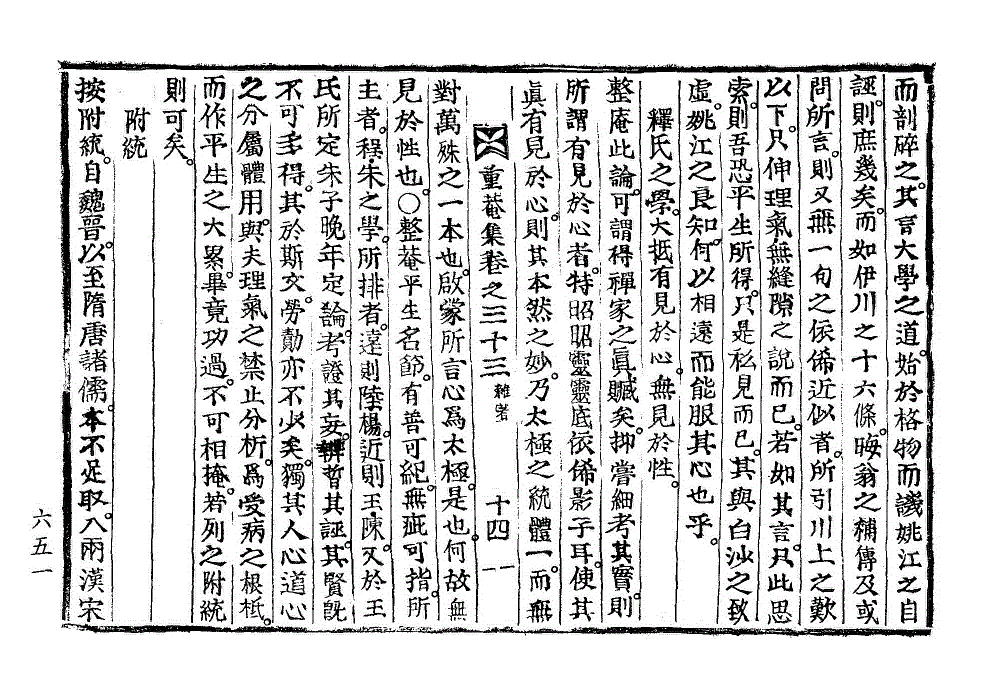 而剖碎之。其言大学之道。始于格物而讥姚江之自诬。则庶几矣。而如伊川之十六条。晦翁之补传及或问所言。则又无一句之依俙近似者。所引川上之叹以下。只伸理气无缝隙之说而已。若如其言。只此思索。则吾恐平生所得。只是私见而已。其与白沙之致虚。姚江之良知。何以相远而能服其心也乎。
而剖碎之。其言大学之道。始于格物而讥姚江之自诬。则庶几矣。而如伊川之十六条。晦翁之补传及或问所言。则又无一句之依俙近似者。所引川上之叹以下。只伸理气无缝隙之说而已。若如其言。只此思索。则吾恐平生所得。只是私见而已。其与白沙之致虚。姚江之良知。何以相远而能服其心也乎。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
整庵此论。可谓得禅家之真赃矣。抑尝细考其实。则所谓有见于心者。特昭昭灵灵底依俙影子耳。使其真有见于心。则其本然之妙。乃太极之统体一。而无对万殊之一本也。启蒙所言心为太极。是也。何故无见于性也。○整庵平生名节。有善可纪。无疵可指。所主者。程,朱之学。所排者。远则陆,杨。近则王,陈。又于王氏所定朱子晚年定论。考證其妄。辨晢其诬。其贤既不可多得。其于斯文。劳绩亦不少矣。独其人心道心之分属体用。与夫理气之禁止分析。为受病之根柢。而作平生之大累。毕竟功过。不可相掩。若列之附统则可矣。
学统考○附统
按附统。自魏晋。以至隋唐诸儒。本不足取。入两汉宋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2H 页
 明之人。滥觞亦多矣。览者宜察之。
明之人。滥觞亦多矣。览者宜察之。左丘明
左氏作春秋传。虽有夸诬淫艳之失。其发挥圣经。嘉惠后人之功。亦不可没。列之附统无疑。但左丘明。耻巧言令色者也。而左传。实犯所耻。故朱子不信其为丘明之书。今以为丘明。未安甚矣。
公明宣
按公明宣。躬行如此。可谓贤矣。但三年不读书。终是病痛。后来传道之责。让与子思而己不得与焉。岂无所由而然哉。曾子于宣之对。当许其所能而勉其所阙。岂宜避席称谢而便休耶。此恐记者之疏也。曾子避席以下。依小学删之为宜。而熊氏不检。可恨。
辕固。○辕固治诗。为景帝博士。与黄生。争论于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上下之分也。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下。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即天下之位非耶。于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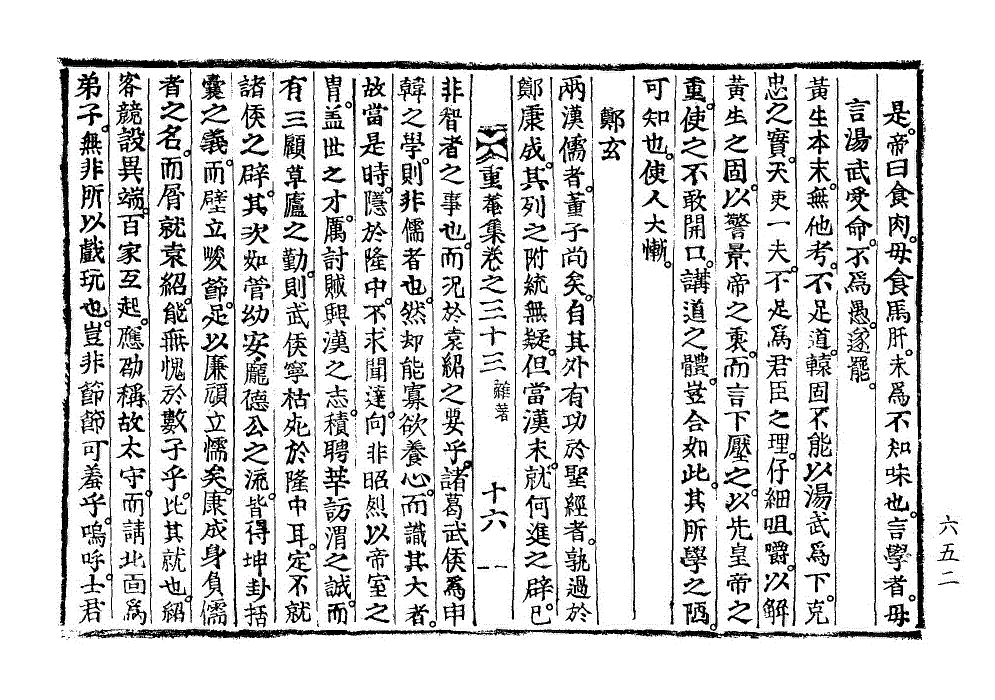 是。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是。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黄生本末。无他考。不足道。辕固不能以汤武为下。克忠之实。天吏一夫。不足为君臣之理。仔细咀嚼。以解黄生之固。以警景帝之衷。而言下压之。以先皇帝之重。使之不敢开口。讲道之体。岂合如此。其所学之陋。可知也。使人大惭。
郑玄
两汉儒者。董子尚矣。自其外有功于圣经者。孰过于郑康成。其列之附统无疑。但当汉末。就何进之辟。已非智者之事也。而况于袁绍之要乎。诸葛武侯为申韩之学。则非儒者也。然却能寡欲养心。而识其大者。故当是时。隐于隆中。不求闻达。向非昭烈以帝室之胄。盖世之才。厉讨贼兴汉之志。积聘莘访渭之诚。而有三顾草庐之勤。则武侯宁枯死于隆中耳。定不就诸侯之辟。其次如管幼安,庞德公之流。皆得坤卦括囊之义。而壁立峻节。足以廉顽立懦矣。康成身负儒者之名。而屑就袁绍。能无愧于数子乎。比其就也。绍客竞设异端。百家互起。应劭称故太守。而请北面为弟子。无非所以戏玩也。岂非节节可羞乎。呜呼。士君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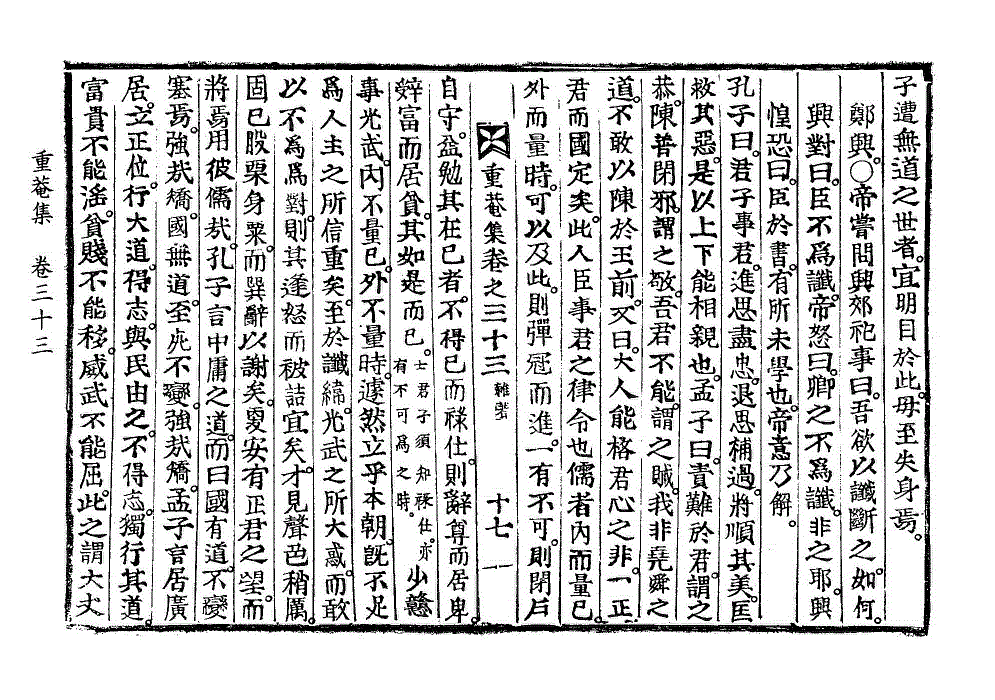 子遭无道之世者。宜明目于此。毋至失身焉。
子遭无道之世者。宜明目于此。毋至失身焉。郑兴。○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如何。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耶。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也。帝意乃解。
孔子曰。君子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是以上下能相亲也。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又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矣。此人臣事君之律令也儒者内而量己。外而量时。可以及此。则弹冠而进。一有不可。则闭户自守。益勉其在己者。不得已而禄仕。则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其如是而已。(士君子须知禄仕。亦有不可为之时。)少戆事光武。内不量己。外不量时。遽然立乎本朝。既不足为人主之所信重矣。至于谶纬。光武之所大惑。而敢以不为为对。则其逢怒而被诘宜矣。才见声色稍厉。固已股栗身粟。而巽辞以谢矣。更安有正君之望。而将焉用彼儒哉。孔子言中庸之道。而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孟子言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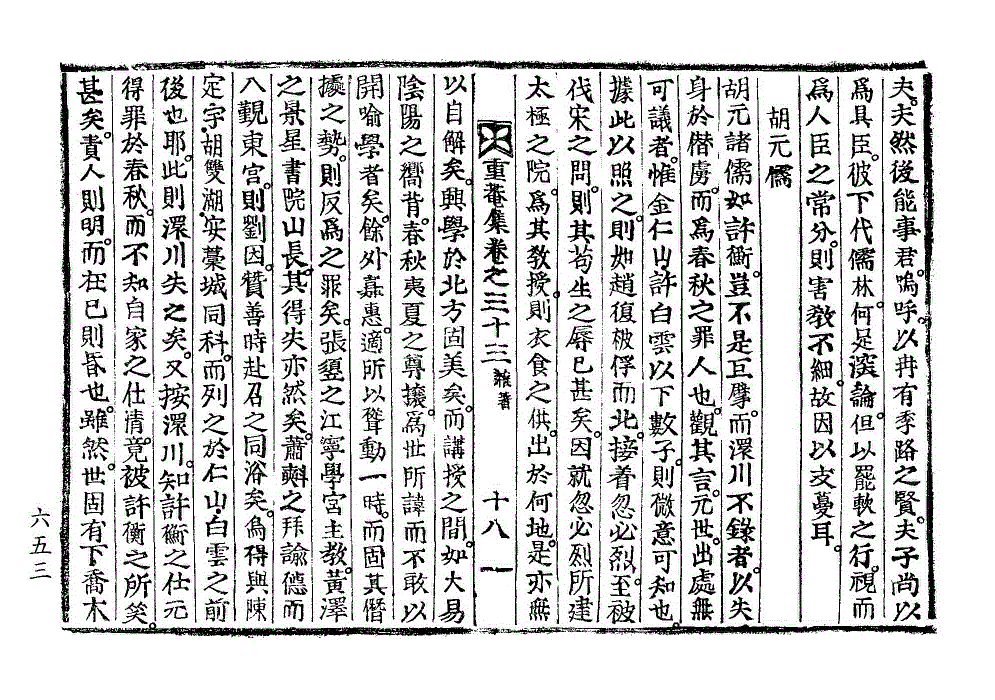 夫。夫然后能事君。呜呼。以冉有季路之贤。夫子尚以为具臣。彼下代儒林。何足深论。但以罢软之行。视而为人臣之常分。则害教不细。故因以支蔓耳。
夫。夫然后能事君。呜呼。以冉有季路之贤。夫子尚以为具臣。彼下代儒林。何足深论。但以罢软之行。视而为人臣之常分。则害教不细。故因以支蔓耳。胡元儒
胡元诸儒如许衡。岂不是巨擘。而澴川不录者。以失身于僭虏。而为春秋之罪人也。观其言。元世。出处无可议者。惟金仁山,许白云以下数子。则微意可知也。据此以照之。则如赵复被俘而北。接着忽必烈。至被伐宋之问。则其苟生之辱已甚矣。因就忽必烈所建太极之院。为其教授。则衣食之供。出于何地。是亦无以自解矣。兴学于北方固美矣。而讲援之间。如大易阴阳之向背。春秋夷夏之尊攘。为世所讳而不敢以开喻学者矣。馀外嘉惠。适所以耸动一时。而固其僭据之势。则反为之罪矣。张䇓之江宁学宫主教。黄泽之景星书院山长。其得失亦然矣。萧𣂏之拜谕德而入觐东宫。则刘因。赞善时赴召之同浴矣。乌得与陈定宇,胡双湖,安藁城同科。而列之于仁山,白云之前后也耶。此则澴川失之矣。又按澴川。知许衡之仕元得罪于春秋。而不知自家之仕清。竟被许衡之所笑。甚矣。责人则明。而在己则昏也。虽然。世固有下乔木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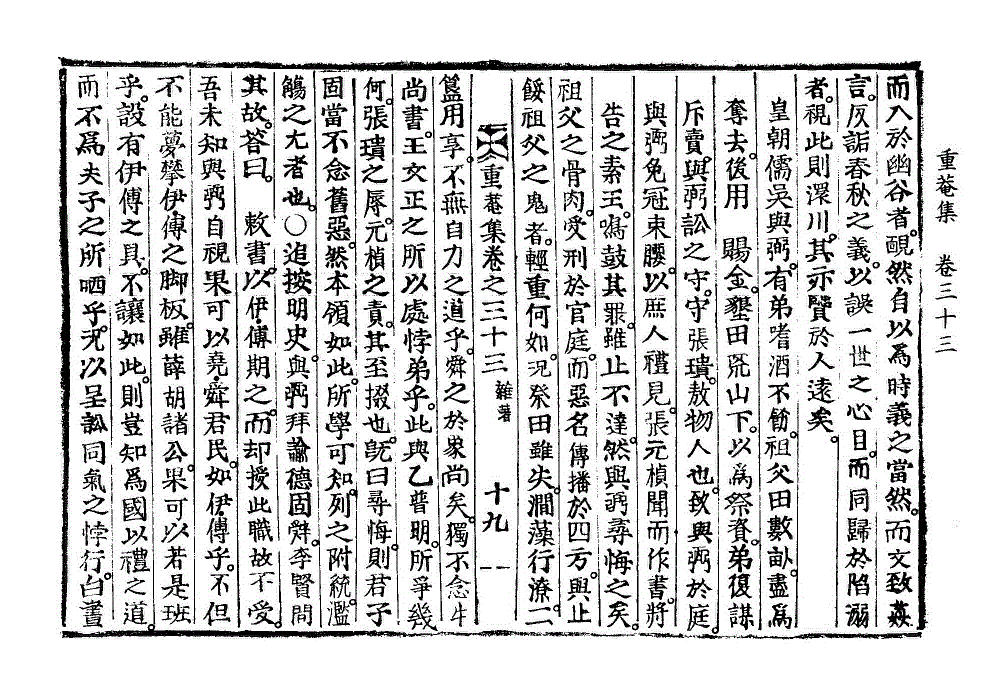 而入于幽谷者。腼然自以为时义之当然。而文致奸言。反诟春秋之义。以误一世之心目。而同归于陷溺者。视此则澴川。其亦贤于人远矣。
而入于幽谷者。腼然自以为时义之当然。而文致奸言。反诟春秋之义。以误一世之心目。而同归于陷溺者。视此则澴川。其亦贤于人远矣。皇朝儒吴与弼。有弟嗜酒不饬。祖父田数亩。尽为夺去。后用 赐金。垦田荒山下。以为祭资。弟复谋斥卖。与弼说之守。守张瑰。敖物人也。致与弼于庭。与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礼见。张元桢闻而作书。将告之素王。鸣鼓其罪。虽止不达。然与弼寻悔之矣。
祖父之骨肉。受刑于官庭。而恶名传播于四方。与止馁祖父之鬼者。轻重何如。况祭田虽失。涧藻行潦。二簋用享。不无自力之道乎。舜之于象尚矣。独不念牛尚书。王文正之所以处悖弟乎。此与乙普明。所争几何。张瑰之辱。元桢之责。其至掇也。既曰寻悔。则君子固当不念旧恶。然本领如此。所学可知。列之附统。滥觞之尤者也。○追按明史。与弼拜谕德固辞。李贤问其故。答曰。 敕书。以伊,传期之。而却授此职故不受。吾未知与弼自视果可以尧,舜君民。如伊,傅乎。不但不能梦攀伊,傅之脚板。虽薛胡诸公。果可以若是班乎。设有伊,傅之具。不让如此。则岂知为国以礼之道。而不为夫子之所哂乎。况以呈讼同气之悖行。白昼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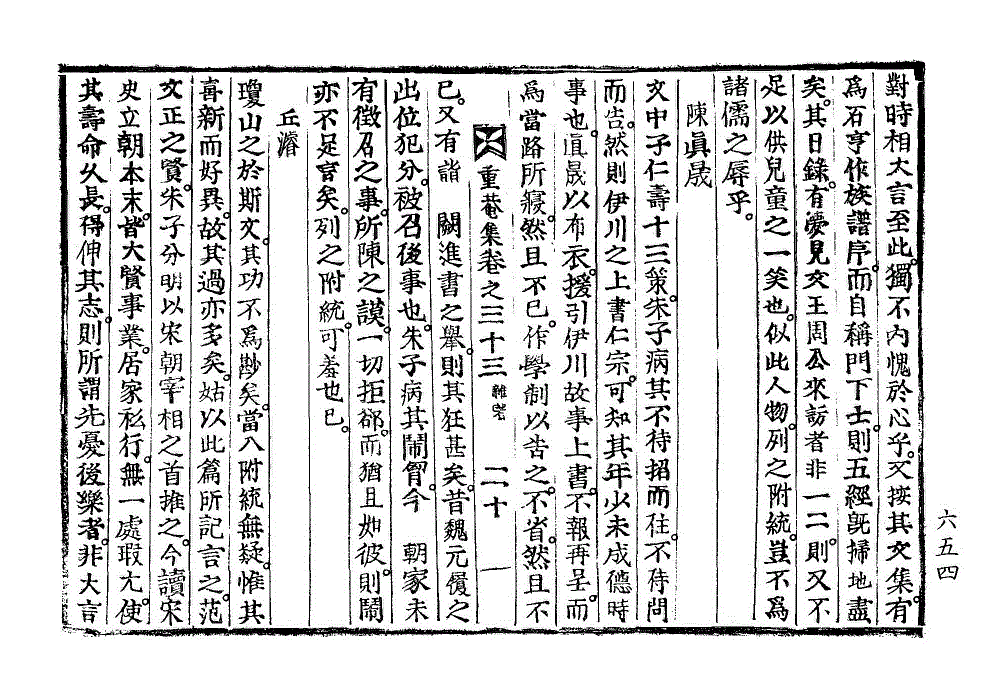 对时相大言至此。独不内愧于心乎。又按其文集。有为石亨作族谱序。而自称门下士。则五经既扫地尽矣。其日录。有梦见文王周公来访者非一二。则又不足以供儿童之一笑也。似此人物。列之附统。岂不为诸儒之辱乎。
对时相大言至此。独不内愧于心乎。又按其文集。有为石亨作族谱序。而自称门下士。则五经既扫地尽矣。其日录。有梦见文王周公来访者非一二。则又不足以供儿童之一笑也。似此人物。列之附统。岂不为诸儒之辱乎。陈真晟
文中子仁寿十三策。朱子病其不待招而往。不待问而告。然则伊川之上书仁宗。可知其年少未成德时事也。真晟以布衣。援引伊川故事上书。不报再呈。而为当路所寝。然且不已。作学制以告之。不省。然且不已。又有诣 阙进书之举。则其狂甚矣。昔魏元履之出位犯分。被召后事也。朱子病其闹胸。今 朝家未有徵召之事。所陈之谟。一切拒郤。而犹且如彼。则闹亦不足言矣。列之附统。可羞也已。
丘浚
琼山之于斯文。其功不为鲜矣。当入附统无疑。惟其喜新而好异。故其过亦多矣。姑以此篇所记言之。范文正之贤。朱子分明以宋朝宰相之首推之。今读宋史立朝本末。皆大贤事业。居家私行。无一处瑕尤。使其寿命久长。得伸其志。则所谓先忧后乐者。非大言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5H 页
 而已。今片言断之。为生事人。岳武穆与金人战。所向无敌。恢复之势。八九分已成。而秦桧构杀。事皆瓦解。史牒所记昭然可考。今反谓未必恢复。桧之作相后本末。有万死之大罪。无一善之可纪。今反谓有功。末造此等持论。一切反常。可惊可骇。不知何故如此。惟欲黜元统。深斥许衡。则所见度越。薛,罗诸公。虽孔,朱复起。当莞尔而笑矣。
而已。今片言断之。为生事人。岳武穆与金人战。所向无敌。恢复之势。八九分已成。而秦桧构杀。事皆瓦解。史牒所记昭然可考。今反谓未必恢复。桧之作相后本末。有万死之大罪。无一善之可纪。今反谓有功。末造此等持论。一切反常。可惊可骇。不知何故如此。惟欲黜元统。深斥许衡。则所见度越。薛,罗诸公。虽孔,朱复起。当莞尔而笑矣。杨守陈
以象以典刑章。为舜命官之辞。以卷耳。为大夫行役之作。以柏舟。为非妇人之作。以郑卫诸诗。为非淫者之作。以丧大记一篇。为仪礼经文。直是狂怪。不忍正视。亦好新尚奇。压倒朱子之心也。尤翁在者。不免于斯文乱贼之诛矣。岂肯谓归诸道。岂肯谓求圣人于言表。岂肯列之附统之中乎。或疑以柏舟。谓非妇人之作。以孔子言。吾于柏舟。见匹夫之不可易者断之。则恐有说矣。是不然。夫子此语。特因柏舟之词。而推见匹夫之守。不可易也。岂此诗之解题耶。理有未明。不能尽乎圣言之意而驱率之。遂绌朱夫子定本。直任胸臆之所裁。则天下岂有难事。此尤翁之于骊尹。所以深恶而痛绝之者也。可戒可戒。又按下文言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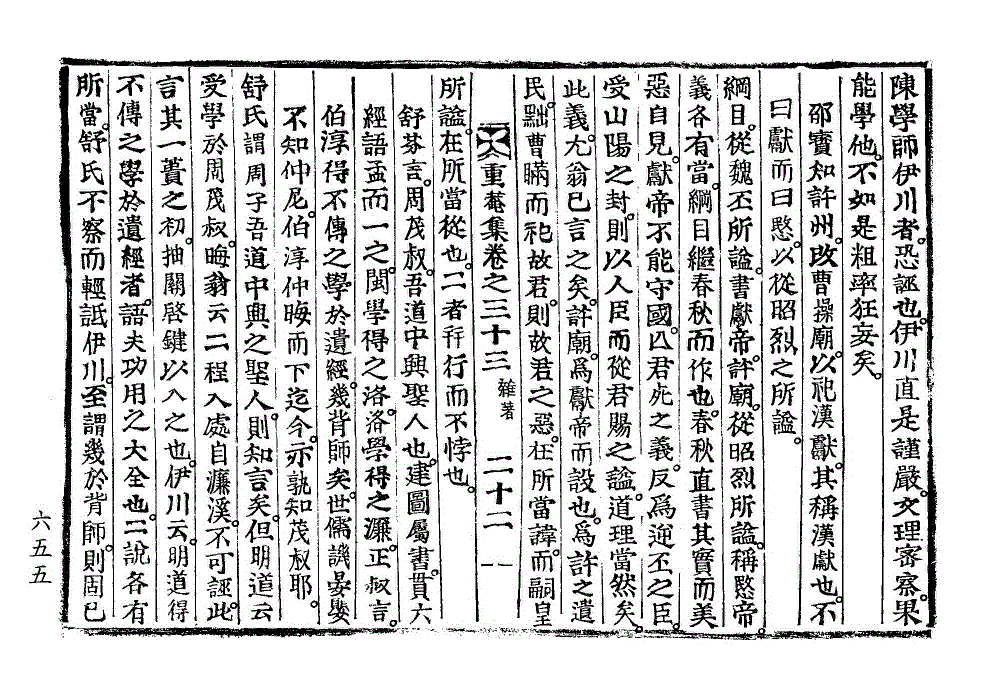 陈学师伊川者。恐诬也。伊川直是谨严。文理密察。果能学他。不如是粗率狂妄矣。
陈学师伊川者。恐诬也。伊川直是谨严。文理密察。果能学他。不如是粗率狂妄矣。邵宝知许州。改曹操庙。以祀汉献。其称汉献也。不曰献而曰悯。以从昭烈之所谥。
纲目。从魏丕所谥。书献帝。许庙。从昭烈所谥。称悯帝。义各有当。纲目继春秋而作也。春秋直书其实而美恶自见。献帝不能守国。亡君死之义。反为逆丕之臣。受山阳之封。则以人臣而从君赐之谥。道理当然矣。此义。尤翁已言之矣。许庙。为献帝而设也。为许之遗民。黜曹瞒而祀故君。则故君之恶。在所当讳。而嗣皇所谥。在所当从也。二者并行而不悖也。
舒芬言。周茂叔。吾道中兴圣人也。建图属书。贯六经语孟而一之。闽学得之洛。洛学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几背师矣。世儒讥晏婴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
舒氏谓周子吾道中兴之圣人。则知言矣。但明道云受学于周茂叔。晦翁云二程入处自濂溪。不可诬。此言其一蒉之初。抽关启键以入之也。伊川云。明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者。语夫功用之大全也。二说各有所当。舒氏不察而轻诋伊川。至谓几于背师。则固已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6H 页
 轻肆而无忌惮矣。至于朱子。则推尊周子以为上接洙泗之统。下启河洛之源。为二陆发明太极之旨。不遗馀力。又就图书。解剥疏释。靡有馀蕴。今其书俱在。何可诬也。今乃并程朱而致不满之意以为晏婴不知仲尼之类。则又似病狂人说话。其亦怪矣。
轻肆而无忌惮矣。至于朱子。则推尊周子以为上接洙泗之统。下启河洛之源。为二陆发明太极之旨。不遗馀力。又就图书。解剥疏释。靡有馀蕴。今其书俱在。何可诬也。今乃并程朱而致不满之意以为晏婴不知仲尼之类。则又似病狂人说话。其亦怪矣。学统考○杂统
陈白沙。○敬斋胡氏曰。陈公甫言。静中养。出端倪。又言藏而发。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
白沙之学。本领不是。故可如此论诋。不然。静中养出端倪。岂不是静中有物功夫。藏而后发。岂不是翕聚而发散。以静而制动之理。须知本领不是。则虽有一言一句同处。只是诐淫。
又曰。气之发用处即是神。公甫说。无动非神。他只窥测至此。不识里面本体。故认气为理。
陈氏无动非神。诚认气为理而发也。不可不辨。若惩羹吹齑。凡言神处。欲一切以气之发用断之。禁不得。以理言。则又矫枉过直而有种种窒碍处。朱子答杜仁仲书云。神是理之发用而乘气以出入。故易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来喻却将神字。全作气者。恐误耳。周子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神妙万物。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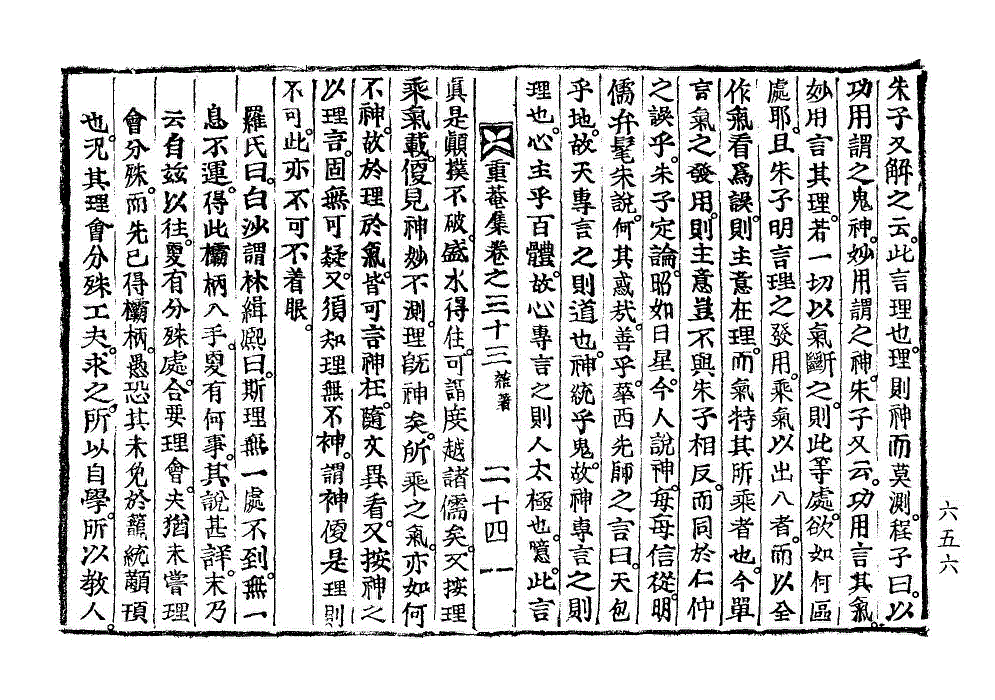 朱子又解之云。此言理也。理则神而莫测。程子曰。以功用谓之鬼神。妙用谓之神。朱子又云。功用言其气。妙用言其理。若一切以气断之。则此等处。欲如何区处耶。且朱子明言理之发用。乘气以出入者。而以全作气看为误。则主意在理。而气特其所乘者也。今单言气之发用。则主意岂不与朱子相反。而同于仁仲之误乎。朱子定论。昭如日星。今人说神。每每信从。明儒弁髦朱说。何其惑哉。善乎。华西先师之言曰。天包乎地。故天专言之则道也。神统乎鬼。故神专言之则理也。心主乎百体。故心专言之则人太极也。噫。此言真是颠扑不破。盛水得住。可谓度越诸儒矣。又按理乘气载。便见神妙不测。理既神矣。所乘之气。亦如何不神。故于理于气。皆可言神在。随文异看。又按神之以理言。固无可疑。又须知理无不神。谓神便是理则不可。此亦不可不着眼。
朱子又解之云。此言理也。理则神而莫测。程子曰。以功用谓之鬼神。妙用谓之神。朱子又云。功用言其气。妙用言其理。若一切以气断之。则此等处。欲如何区处耶。且朱子明言理之发用。乘气以出入者。而以全作气看为误。则主意在理。而气特其所乘者也。今单言气之发用。则主意岂不与朱子相反。而同于仁仲之误乎。朱子定论。昭如日星。今人说神。每每信从。明儒弁髦朱说。何其惑哉。善乎。华西先师之言曰。天包乎地。故天专言之则道也。神统乎鬼。故神专言之则理也。心主乎百体。故心专言之则人太极也。噫。此言真是颠扑不破。盛水得住。可谓度越诸儒矣。又按理乘气载。便见神妙不测。理既神矣。所乘之气。亦如何不神。故于理于气。皆可言神在。随文异看。又按神之以理言。固无可疑。又须知理无不神。谓神便是理则不可。此亦不可不着眼。罗氏曰。白沙谓林缉熙曰。斯理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说甚详。末乃云自玆以往。更有分殊处。合要理会。夫犹未尝理会分殊。而先已得把柄。愚恐其未免于笼统颟顸也。况其理会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学。所以教人。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7H 页
 皆无实事可见。得非欲稍自别于禅学。而姑为是言耶。
皆无实事可见。得非欲稍自别于禅学。而姑为是言耶。罗氏谓白沙。未尝理会分殊。先得把柄。恐未免笼统颟顸。又云。求之自学教人。理会分殊。皆无实事可见。是欲稍自别于禅学。姑为是言者。深中陈氏之差矣。愚则又谓斯理。谓之无处不有。无时不然。则知言矣。今谓之无不到无不运。则是理有情意造作运用也。岂得为物则乎。只此到字运字。可见认气为理。假令理会分殊得来。只是作用是性底规模意思。非理会事物当然之则。此如何讳得。虽然。罗氏恶理气之有分。而主一物之说。则其所谓理一亦气也。分殊亦气也。然则罗氏之所谓实事所争。恐亦五十百步之间也。
整庵复湛甘泉书曰。今以白沙为禅学。诚有据也。白沙之言。有曰。道至无而动。至近而神。又曰。致虚。所以立本也。执事从而发明之曰。至无。无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玆非可据之实乎。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今乃认不测之神。以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7L 页
 为天理则所谓道者。果何物耶。其于大传。与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惟敬而无失。最尽是则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无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谓致虚所以立本。其与中庸与明道之言。又不合矣。
为天理则所谓道者。果何物耶。其于大传。与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惟敬而无失。最尽是则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无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谓致虚所以立本。其与中庸与明道之言。又不合矣。理是事物当然之则。故有善无恶。神是此理之乘气流行者也。乘气也故有真有妄。甘泉不知辨此。而唤神作理。则固失之矣。至于阴阳不测之谓神。自章首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串贯来。而为结语则是言道之体用。其妙如此。岂可为神是气之證乎。明道之训。以无声无臭起头。则是言无极之真也。然则其体谓之易。无极之体质也。在人则心也。其理谓之道。无极之准则也。在人则性也。其用谓之神。无极之妙用也。在人则情也。一以贯之。是无极之注脚也。又可为神。是气之證乎。其引中庸明道之训。而斥致虚立本之谬则是矣。但世之人。不敬而失中者。滔滔皆然。何也。有气故也。气拘而不知检。则不能持其敬矣。不能持其敬。则心体不免于偏倚而失中矣。然则理有善无恶。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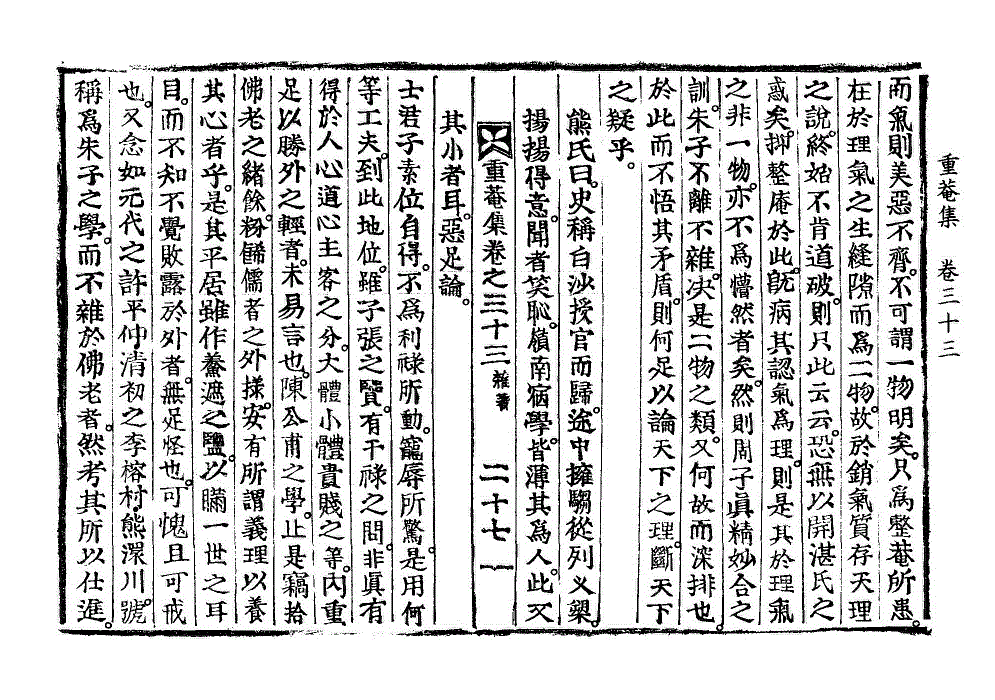 而气则美恶不齐。不可谓一物明矣。只为整庵所患。在于理气之生缝隙而为二物。故于销气质存天理之说。终始不肯道破。则只此云云。恐无以开湛氏之惑矣。抑整庵于此。既病其认气为理。则是其于理气之非一物。亦不为懵然者矣。然则周子真精妙合之训。朱子不离不杂。决是二物之类。又何故而深排也。于此而不悟其矛盾。则何足以论天下之理。断天下之疑乎。
而气则美恶不齐。不可谓一物明矣。只为整庵所患。在于理气之生缝隙而为二物。故于销气质存天理之说。终始不肯道破。则只此云云。恐无以开湛氏之惑矣。抑整庵于此。既病其认气为理。则是其于理气之非一物。亦不为懵然者矣。然则周子真精妙合之训。朱子不离不杂。决是二物之类。又何故而深排也。于此而不悟其矛盾。则何足以论天下之理。断天下之疑乎。熊氏曰。史称白沙授官而归。途中拥驺从列叉槊扬扬得意。闻者笑耻。岭南宿学。皆薄其为人。此又其小者耳。恶足论。
士君子素位自得。不为利禄所动。宠辱所惊。是用何等工夫。到此地位。虽子张之贤。有干禄之问。非真有得于人心道心主客之分。大体小体贵贱之等。内重足以胜外之轻者。未易言也。陈公甫之学。止是窃拾佛老之绪馀。粉饰儒者之外㨾。安有所谓义理以养其心者乎。是其平居虽作鲞遮之盐。以瞒一世之耳目。而不知不觉败露于外者。无足怪也。可愧且可戒也。又念如元代之许平仲,清初之李榕村,熊澴川。号称为朱子之学。而不杂于佛老者。然考其所以仕进。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8L 页
 则又不识夷夏阴阳向背之分。虽无扬扬于道路之迹。而反为公甫辈人所笑耻。审矣。生为夷狄之人。死为夷狄之鬼。又何暇于薄人笑人也哉。
则又不识夷夏阴阳向背之分。虽无扬扬于道路之迹。而反为公甫辈人所笑耻。审矣。生为夷狄之人。死为夷狄之鬼。又何暇于薄人笑人也哉。王阳明。○罗氏曰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实良知良能之说。其义甚明。盖知能乃人心之妙用。爱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虑而自如此。故谓之良。近时有以良知为天理者。然则爱敬果何物乎。
王氏以良知为天理者。不过假孟子说为重。而以知觉运动为性。更不理会仁义礼智之实体。事物散殊之当然。是以陷于猖狂自恣。而为圣门之罪人耳。不然。良知是人心之妙用。诚如罗说。而朱夫子分明说妙用。言其理则以良知为理者有何不可。罗氏谓以良知为天理。则爱敬果何物。殊不知当爱当敬。事物之实理准则也。知其当爱而爱之。知其当敬而敬之。吾心之主宰妙用也。物我一理。内外一贯。故合而言之。则天理之全部也。此宜潜玩。○又按理有以自然言者。有以当然言者。阳明致良知废格致。只为守得那自然。不知有当然。所以为异端邪说。
又曰。王伯安答萧惠云。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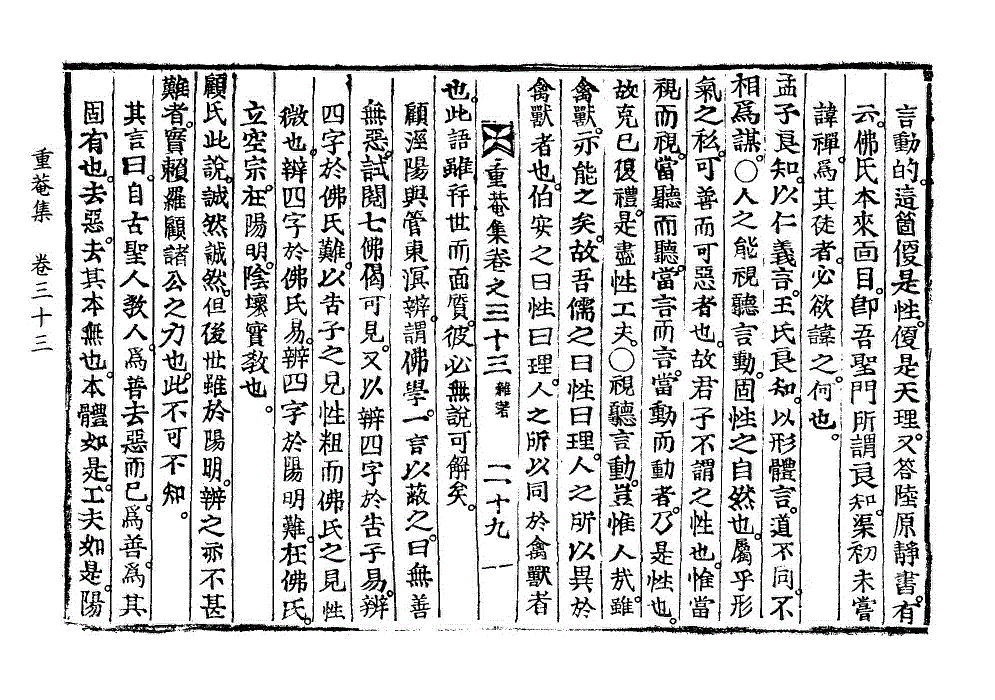 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陆原静书。有云。佛氏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渠初未尝讳禅。为其徒者。必欲讳之。何也。
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陆原静书。有云。佛氏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渠初未尝讳禅。为其徒者。必欲讳之。何也。孟子良知。以仁义言。王氏良知。以形体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人之能视听言动。固性之自然也。属乎形气之私。可善而可恶者也。故君子不谓之性也。惟当视而视。当听而听。当言而言。当动而动者。乃是性也。故克己复礼。是尽性工夫。○视听言动。岂惟人哉。虽禽兽。亦能之矣。故吾儒之曰性曰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也。伯安之曰性曰理。人之所以同于禽兽者也。此语虽并世而面质。彼必无说可解矣。
顾泾阳与管东溟辨。谓佛学。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试阅七佛偈可见。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难。以告子之见性粗而佛氏之见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在佛氏。立空宗。在阳明。阴坏实教也。
顾氏此说。诚然诚然。但后世虽于阳明。辨之亦不甚难者。实赖罗顾诸公之力也。此不可不知。
其言曰。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本体如是。工夫如是。阳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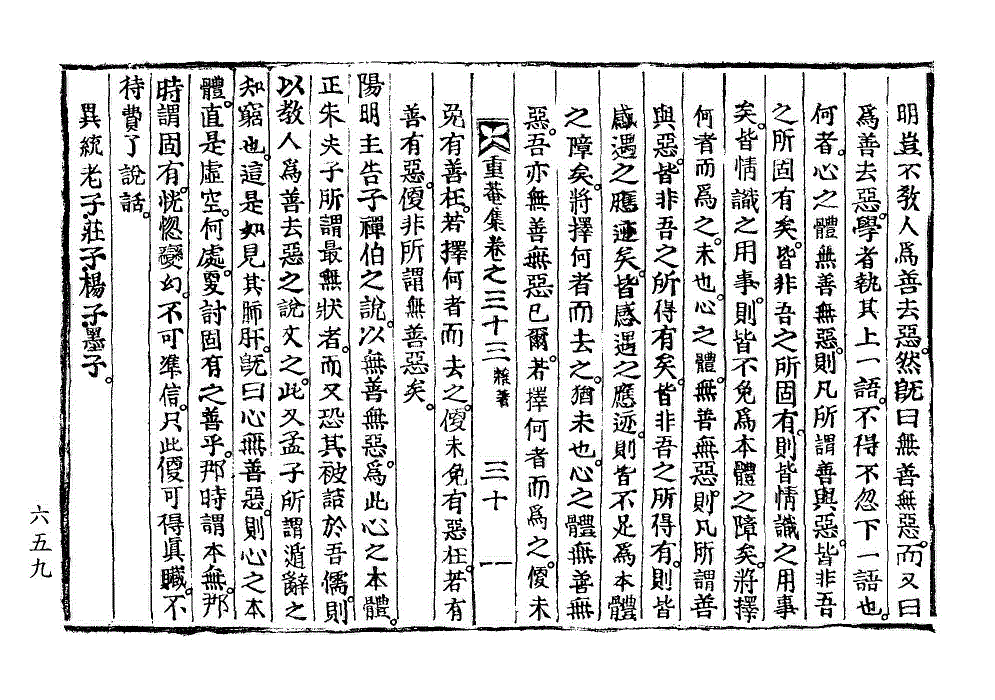 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下一语也。何者。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则皆情识之用事矣。皆情识之用事。则皆不免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为之。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则皆感遇之应迹矣。皆感遇之应迹。则皆不足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去之。犹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吾亦无善无恶已尔。若择何者而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择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恶在。若有善有恶。便非所谓无善恶矣。
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下一语也。何者。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则皆情识之用事矣。皆情识之用事。则皆不免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为之。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则皆感遇之应迹矣。皆感遇之应迹。则皆不足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去之。犹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吾亦无善无恶已尔。若择何者而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择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恶在。若有善有恶。便非所谓无善恶矣。阳明主告子禅伯之说。以无善无恶。为此心之本体。正朱失子所谓最无状者。而又恐其被诘于吾儒。则以教人为善去恶之说文之。此又孟子所谓遁辞之知穷也。这是如见其肺肝。既曰心无善恶。则心之本体。直是虚空。何处。更讨固有之善乎。那时谓本无。那时谓固有。恍惚变幻。不可准信。只此便可得真赃。不待费了说话。
学统考○异统
老子,庄子,杨子,墨子。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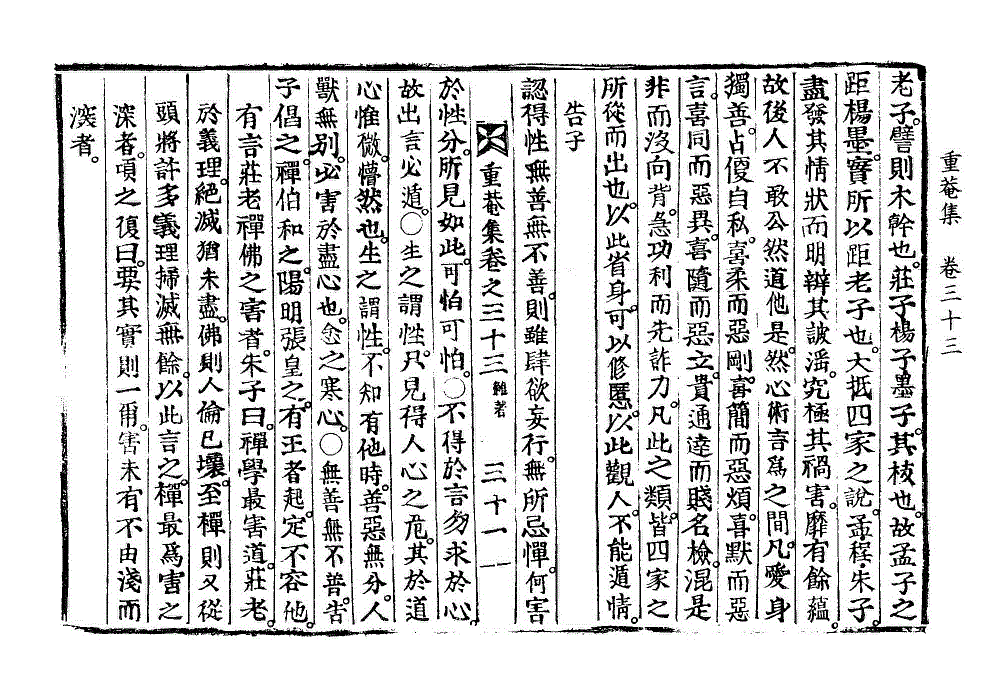 老子。譬则木干也。庄子,杨子,墨子。其枝也。故孟子之距杨墨。实所以距老子也。大抵四家之说。孟,程,朱子。尽发其情状而明辨其诐淫。究极其祸害。靡有馀蕴。故后人不敢公然道他是。然心术言为之间。凡爱身独善。占便自私。喜柔而恶刚。喜简而恶烦。喜默而恶言。喜同而恶异。喜随而恶立。贵通达而贱名检。混是非而没向背。急功利而先诈力。凡此之类。皆四家之所从而出也。以此省身。可以修慝。以此观人。不能遁情。
老子。譬则木干也。庄子,杨子,墨子。其枝也。故孟子之距杨墨。实所以距老子也。大抵四家之说。孟,程,朱子。尽发其情状而明辨其诐淫。究极其祸害。靡有馀蕴。故后人不敢公然道他是。然心术言为之间。凡爱身独善。占便自私。喜柔而恶刚。喜简而恶烦。喜默而恶言。喜同而恶异。喜随而恶立。贵通达而贱名检。混是非而没向背。急功利而先诈力。凡此之类。皆四家之所从而出也。以此省身。可以修慝。以此观人。不能遁情。告子
认得性无善无不善。则虽肆欲妄行。无所忌惮。何害于性分。所见如此。可怕可怕。○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故出言必遁。○生之谓性。只见得人心之危。其于道心惟微。懵然也。生之谓性。不知有他时。善恶无分。人兽无别。必害于尽心也。念之寒心。○无善无不善。告子倡之。禅伯和之。阳明张皇之。有王者起。定不容他。
有言庄老禅佛之害者。朱子曰。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馀。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顷之复曰。要其实则一尔。害未有不由浅而深者。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60L 页
 按佛氏之教。其说始甚浅陋。只资诳诱闾巷之夫妇而已。楚王英之好之。其亦不学无识。类闾巷之夫妇故然耳。兼且燃顶烧臂。许多受戒。断饮绝色。许多防欲。皆是不近人情。未可以科率天下之人。则宜若无深长之虑。而一遇中国文人才子尚奇好事之辈。剽窃老氏之言。敷演修饰。转相传授。则非复畴昔之浅陋矣。加之达摩入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则其学益以高妙。而酷近于理矣。于是天下之高才明智。莫不靡然从之。而公私贤愚。男女贵贱。一出于佛大宇之下。无复撮土之乾净。则千有馀年之间。万国生灵。受涂炭鱼肉之祸者。盖不可以言语文字尽之矣。今欧罗巴之教。又异于彼。姑以目接而耳得者言之。其高者如利玛窦艾儒略之书。已非佛书四十二章之比也。其天度历法。奇技淫巧。尚鬼喜幻。眩惑天下之耳目。歆动天下之心思者。又佛氏之所无也。其入之以合从富强之说。悦之以通货冒色之欲者。又与佛氏之受戒防欲。至于不近人情者。不趐如昼夜之相反矣。盖其一贤愚通上下。岁月浸润。诱引以入之者。为网甚密。一目不疏。使六合之内。欣然同归而无异辞。又佛氏之所不能致也。于是时也。若有文学之士。负
按佛氏之教。其说始甚浅陋。只资诳诱闾巷之夫妇而已。楚王英之好之。其亦不学无识。类闾巷之夫妇故然耳。兼且燃顶烧臂。许多受戒。断饮绝色。许多防欲。皆是不近人情。未可以科率天下之人。则宜若无深长之虑。而一遇中国文人才子尚奇好事之辈。剽窃老氏之言。敷演修饰。转相传授。则非复畴昔之浅陋矣。加之达摩入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则其学益以高妙。而酷近于理矣。于是天下之高才明智。莫不靡然从之。而公私贤愚。男女贵贱。一出于佛大宇之下。无复撮土之乾净。则千有馀年之间。万国生灵。受涂炭鱼肉之祸者。盖不可以言语文字尽之矣。今欧罗巴之教。又异于彼。姑以目接而耳得者言之。其高者如利玛窦艾儒略之书。已非佛书四十二章之比也。其天度历法。奇技淫巧。尚鬼喜幻。眩惑天下之耳目。歆动天下之心思者。又佛氏之所无也。其入之以合从富强之说。悦之以通货冒色之欲者。又与佛氏之受戒防欲。至于不近人情者。不趐如昼夜之相反矣。盖其一贤愚通上下。岁月浸润。诱引以入之者。为网甚密。一目不疏。使六合之内。欣然同归而无异辞。又佛氏之所不能致也。于是时也。若有文学之士。负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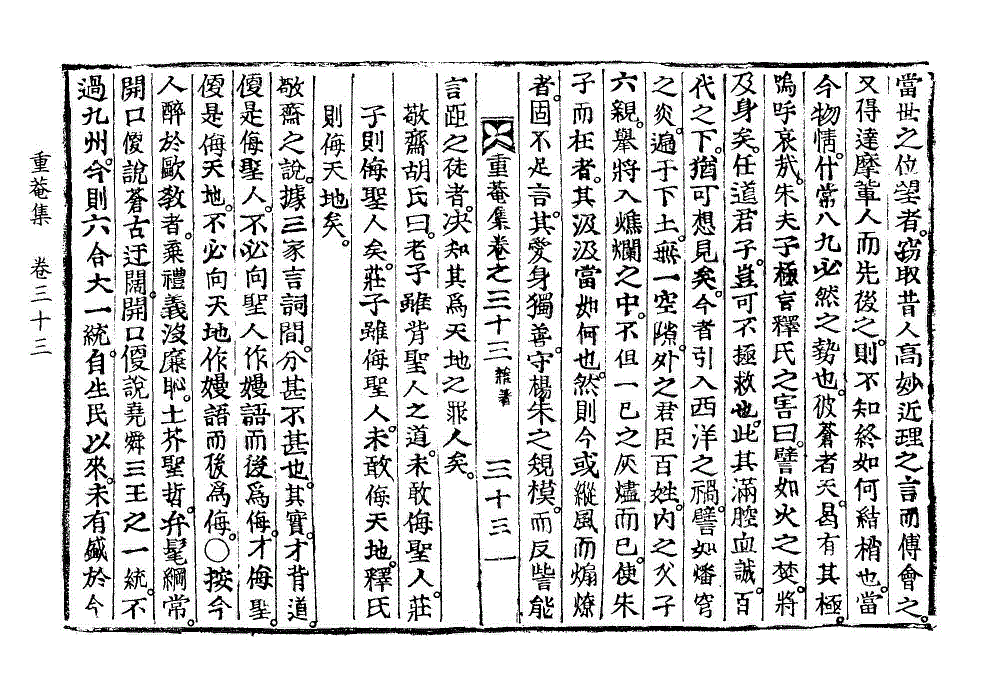 当世之位望者。窃取昔人高妙近理之言而傅会之。又得达摩辈人而先后之。则不知终如何结梢也。当今物情。什常八九必然之势也。彼苍者天。曷有其极。呜呼哀哉。朱夫子极言释氏之害曰。譬如火之焚。将及身矣。任道君子。岂可不极救也。此其满腔血诚。百代之下。犹可想见矣。今者引入西洋之祸。譬如燔穹之炎。遍于下土。无一空隙。外之君臣百姓。内之父子六亲。举将入燋烂之中。不但一己之灰烬而已。使朱子而在者。其汲汲当如何也。然则今或纵风而煽燎者。固不足言。其爱身独善。守杨,朱之规模。而反訾能言距之徒者。决知其为天地之罪人矣。
当世之位望者。窃取昔人高妙近理之言而傅会之。又得达摩辈人而先后之。则不知终如何结梢也。当今物情。什常八九必然之势也。彼苍者天。曷有其极。呜呼哀哉。朱夫子极言释氏之害曰。譬如火之焚。将及身矣。任道君子。岂可不极救也。此其满腔血诚。百代之下。犹可想见矣。今者引入西洋之祸。譬如燔穹之炎。遍于下土。无一空隙。外之君臣百姓。内之父子六亲。举将入燋烂之中。不但一己之灰烬而已。使朱子而在者。其汲汲当如何也。然则今或纵风而煽燎者。固不足言。其爱身独善。守杨,朱之规模。而反訾能言距之徒者。决知其为天地之罪人矣。敬斋胡氏曰。老子虽背圣人之道。未敢侮圣人。庄子则侮圣人矣。庄子虽侮圣人。未敢侮天地。释氏则侮天地矣。
敬斋之说。据三家言词间。分甚不甚也。其实。才背道。便是侮圣人。不必向圣人作嫚语而后为侮。才侮圣。便是侮天地。不必向天地作嫚语而后为侮。○按今人醉于欧教者。弃礼义没廉耻。土芥圣哲。弁髦纲常。开口便说苍古迂阔。开口便说尧舜三王之一统。不过九州。今则六合大一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今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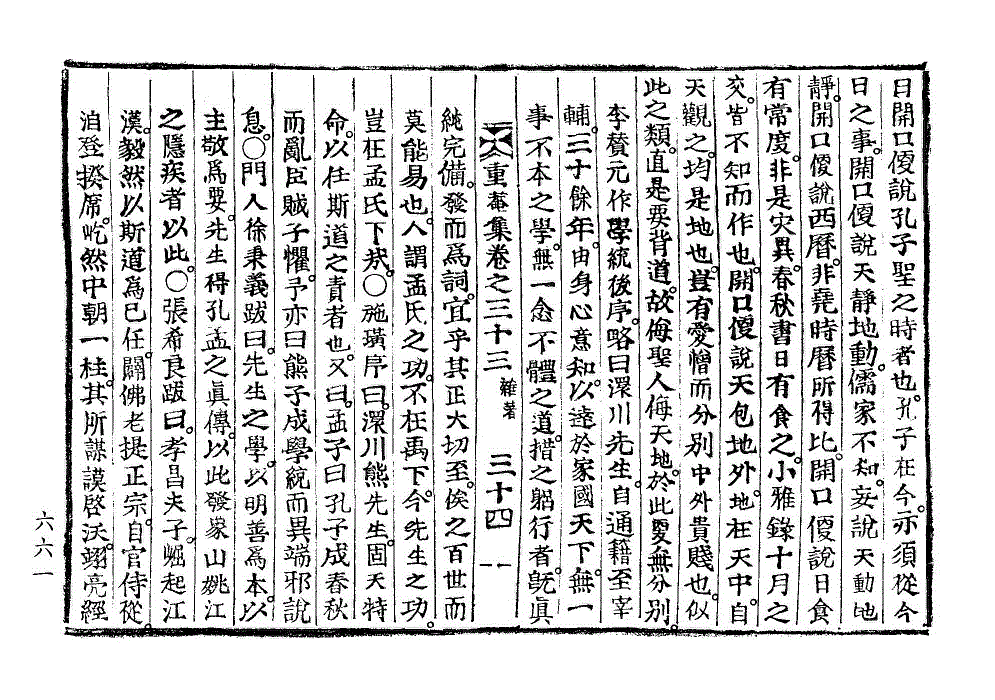 日开口便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在今。亦须从今日之事。开口便说天静地动。儒家不知。妄说天动地静。开口便说西历。非尧时历所得比。开口便说日食有常度。非是灾异。春秋书日有食之。小雅录十月之交。皆不知而作也。开口便说天包地外。地在天中。自天观之。均是地也。岂有爱憎而分别中外贵贱也。似此之类。直是要背道。故侮圣人侮天地。于此更无分别。
日开口便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在今。亦须从今日之事。开口便说天静地动。儒家不知。妄说天动地静。开口便说西历。非尧时历所得比。开口便说日食有常度。非是灾异。春秋书日有食之。小雅录十月之交。皆不知而作也。开口便说天包地外。地在天中。自天观之。均是地也。岂有爱憎而分别中外贵贱也。似此之类。直是要背道。故侮圣人侮天地。于此更无分别。李赞元作学统后序。略曰澴川先生。自通籍至宰辅。三十馀年。由身心意知。以达于家国天下。无一事不本之学。无一念不体之道。措之躬行者。既真纯完备。发而为词。宜乎其正大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人谓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岂在孟氏下哉。○施璜序曰。澴川熊先生。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责者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予亦曰熊子成学统而异端邪说息。○门人徐秉义跋曰。先生之学。以明善为本。以主敬为要。先生得孔孟之真传。以此发象山姚江之隐疾者以此。○张希良跋曰。孝昌夫子。崛起江汉。毅然以斯道为己任。辟佛老提正宗。自官侍从。洎登揆席。屹然中朝一柱。其所谋谟启沃。翊亮经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62H 页
 纶。都从体认天理中出。又曰。学统之书出而后。二帝三王传心之要。危微几希。绝续之辨。昭然可寻。非夫子道参太极。学集大成。何以臻此。
纶。都从体认天理中出。又曰。学统之书出而后。二帝三王传心之要。危微几希。绝续之辨。昭然可寻。非夫子道参太极。学集大成。何以臻此。按学统序跋。其作者本不足以为世轻重。则其言之得失。不足深校览之。只合一笑也。然褊邦无识之辈。以出于中国儒者之手。故仰之或如崇山巨岳。则其势必信之。信之则为害亦不轻矣。盖彼虏以女真种子。再据中国。使天下毁冠裂裳。薙发左衽。则其势必臲卼不安。未可以高枕而卧。故至子康熙。外示崇儒重道之名。延揽天下之士。号为程朱之学者。或致之经幄。或跻之崇班。或使之编书。要以此牢笼天下之名士。而阴夺英雄之气。非出于诚心也。不然。以康熙之才智。得李光地熊赐履若干辈而致之于朝。明示修德立政。用夏变夷。脱落荄甲。扫洗腥膻之意。则彼数子者。皆汉人也。如之何其不欣然奉承。旁招俊乂而赞成之也。惜乎康熙。渠父之子。渠祖之孙。初未有此心。而数子者不过为宠利所动。笼络所入。复蹈许衡吴澄之辙迹。则动不动。为康熙之使唤而已。编辑学统。亦其一事也。虽然。即书而考之。首揭孔子为正统之祖。而以颜曾思孟周程朱子。为正统之宗适。次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第 6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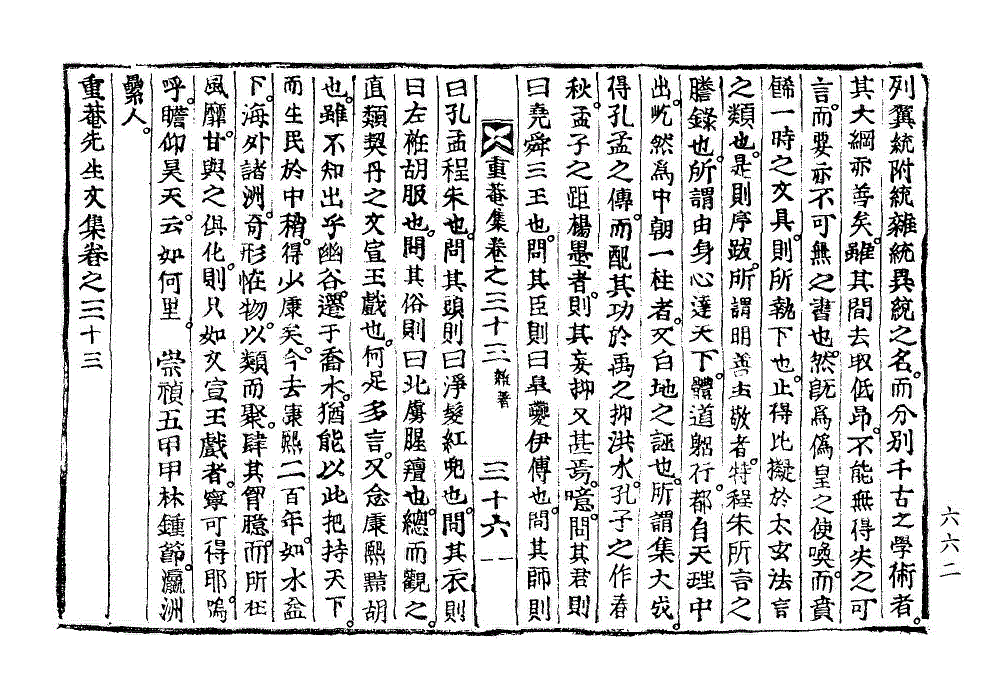 列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之名。而分别千古之学术者。其大纲亦善矣。虽其间去取低昂。不能无得失之可言。而要亦不可无之书也。然既为伪皇之使唤。而贲饰一时之文具。则所执下也。止得比拟于太玄法言之类也。是则序跋。所谓明善主敬者。特程朱所言之誊录也。所谓由身心达天下。体道躬行。都自天理中出。屹然为中朝一柱者。又白地之诬也。所谓集大成。得孔孟之传。而配其功于禹之抑洪水。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距杨墨者。则其妄抑又甚焉。噫。问其君则曰尧舜三王也。问其臣则曰皋夔伊傅也。问其师则曰孔孟程朱也。问其头则曰净发红兜也。问其衣则曰左衽胡服也。问其俗则曰北虏腥膻也。总而观之。直类契丹之文宣王戏也。何足多言。又念康熙黠胡也。虽不知出乎幽谷。迁于乔水。犹能以此把持天下。而生民于中稍。得少康矣。今去康熙二百年。如水益下。海外诸洲。奇形怪物。以类而聚。肆其胸臆。而所在风靡。甘与之俱化。则只如文宣王戏者。宁可得耶。呜呼。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崇祯五甲甲林钟节。瀛洲累人。
列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之名。而分别千古之学术者。其大纲亦善矣。虽其间去取低昂。不能无得失之可言。而要亦不可无之书也。然既为伪皇之使唤。而贲饰一时之文具。则所执下也。止得比拟于太玄法言之类也。是则序跋。所谓明善主敬者。特程朱所言之誊录也。所谓由身心达天下。体道躬行。都自天理中出。屹然为中朝一柱者。又白地之诬也。所谓集大成。得孔孟之传。而配其功于禹之抑洪水。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距杨墨者。则其妄抑又甚焉。噫。问其君则曰尧舜三王也。问其臣则曰皋夔伊傅也。问其师则曰孔孟程朱也。问其头则曰净发红兜也。问其衣则曰左衽胡服也。问其俗则曰北虏腥膻也。总而观之。直类契丹之文宣王戏也。何足多言。又念康熙黠胡也。虽不知出乎幽谷。迁于乔水。犹能以此把持天下。而生民于中稍。得少康矣。今去康熙二百年。如水益下。海外诸洲。奇形怪物。以类而聚。肆其胸臆。而所在风靡。甘与之俱化。则只如文宣王戏者。宁可得耶。呜呼。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崇祯五甲甲林钟节。瀛洲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