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书
书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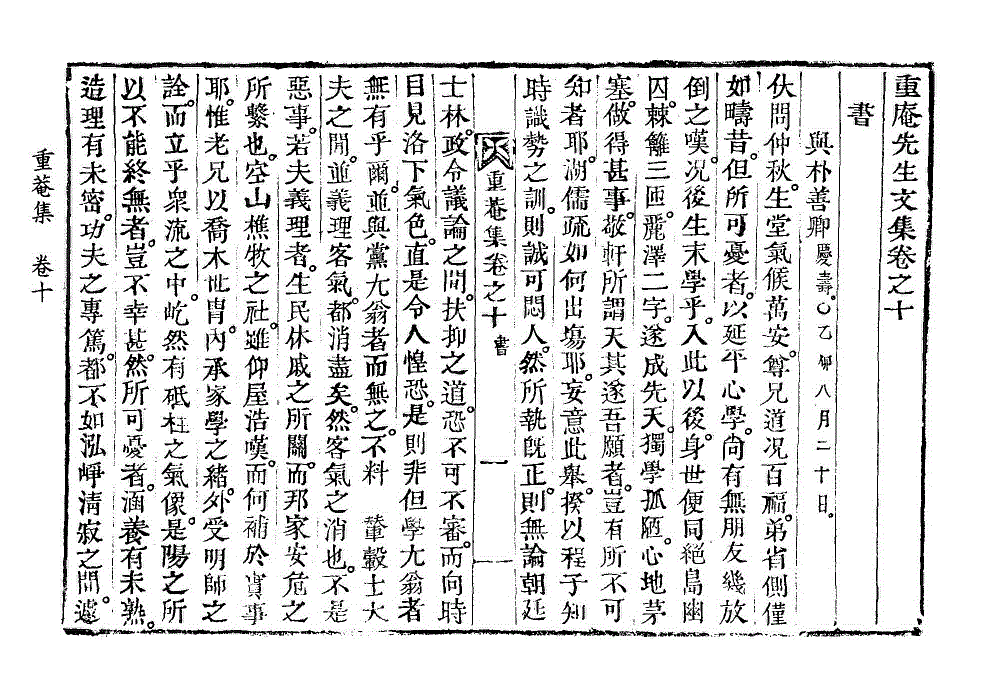 与朴善卿(庆寿。○乙卯八月二十日。)
与朴善卿(庆寿。○乙卯八月二十日。)伏问仲秋。生堂气候万安。尊兄道况百福。弟省侧仅如畴昔。但所可忧者。以延平心学。尚有无朋友几放倒之叹。况后生末学乎。入此以后。身世便同绝岛幽囚。棘篱三匝。丽泽二字。遂成先天。独学孤陋。心地茅塞。做得甚事。敬轩所谓天其遂吾愿者。岂有所不可知者耶。湖儒疏如何出场耶。妄意此举。揆以程子知时识势之训。则诚可闷人。然所执既正。则无论朝廷士林。政令议论之间。扶抑之道。恐不可不审。而向时目见洛下气色。直是令人惶恐。是则非但学尤翁者无有乎尔。并与党尤翁者而无之。不料 辇毂士大夫之閒。并义理客气。都消尽矣。然客气之消也。不是恶事。若夫义理者。生民休戚之所关。而邦家安危之所系也。空山樵牧之社。虽仰屋浩叹。而何补于实事耶。惟老兄以乔木世胄。内承家学之绪。外受明师之诠。而立乎众流之中。屹然有砥枉之气像。是阳之所以不能终无者。岂不幸甚。然所可忧者。涵养有未熟。造理有未密。功夫之专笃。都不如泓峥清寂之间。遽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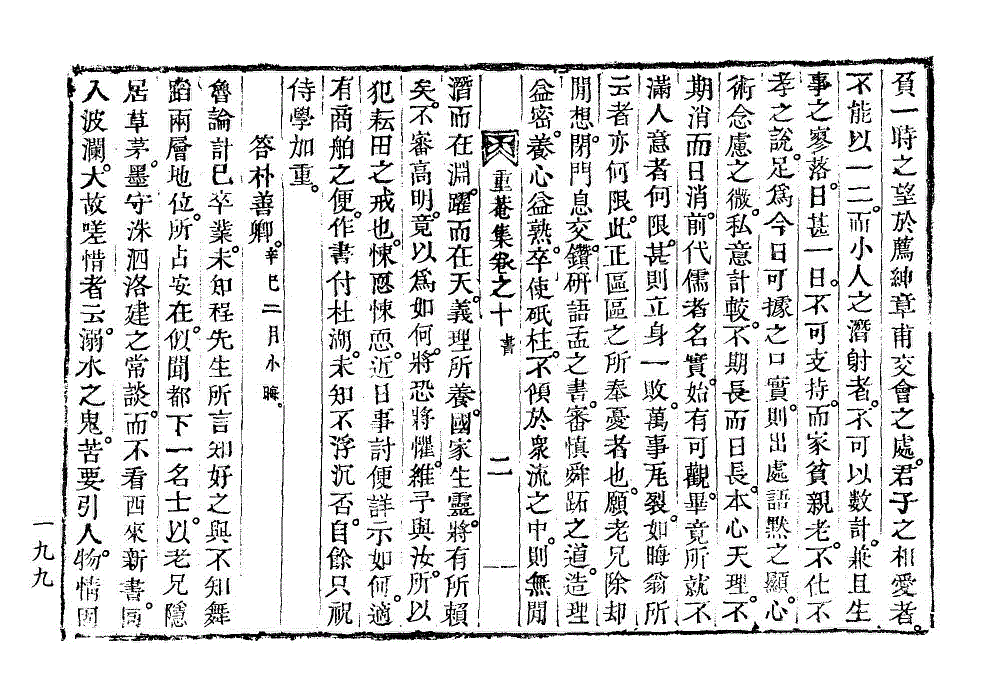 负一时之望于荐绅章甫交会之处。君子之相爱者。不能以一二。而小人之潜射者。不可以数计。兼且生事之寥落。日甚一日。不可支持。而家贫亲老。不仕不孝之说。足为今日可据之口实。则出处语默之显。心术念虑之微。私意计较。不期长而日长。本心天理。不期消而日消。前代儒者名实。始有可观。毕竟所就不满人意者何限。甚则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如晦翁所云者亦何限。此正区区之所奉忧者也。愿老兄除却閒想。闭门息交。钻研语孟之书。审慎舜蹠之道。造理益密。养心益熟。卒使砥柱。不倾于众流之中。则无閒潜而在渊。跃而在天。义理所养。国家生灵。将有所赖矣。不审高明。竟以为如何。将恐将惧。维予与汝。所以犯耘田之戒也。悚恧悚恧。近日事讨便详示如何。适有商舶之便。作书付杜湖。未知不浮沉否。自馀只祝侍学加重。
负一时之望于荐绅章甫交会之处。君子之相爱者。不能以一二。而小人之潜射者。不可以数计。兼且生事之寥落。日甚一日。不可支持。而家贫亲老。不仕不孝之说。足为今日可据之口实。则出处语默之显。心术念虑之微。私意计较。不期长而日长。本心天理。不期消而日消。前代儒者名实。始有可观。毕竟所就不满人意者何限。甚则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如晦翁所云者亦何限。此正区区之所奉忧者也。愿老兄除却閒想。闭门息交。钻研语孟之书。审慎舜蹠之道。造理益密。养心益熟。卒使砥柱。不倾于众流之中。则无閒潜而在渊。跃而在天。义理所养。国家生灵。将有所赖矣。不审高明。竟以为如何。将恐将惧。维予与汝。所以犯耘田之戒也。悚恧悚恧。近日事讨便详示如何。适有商舶之便。作书付杜湖。未知不浮沉否。自馀只祝侍学加重。答朴善卿。(辛巳二月小晦。)
鲁论计已卒业。未知程先生所言知好之与不知舞蹈两层地位。所占安在。似闻都下一名士。以老兄隐居草茅。墨守洙泗洛建之常谈。而不看西来新书。同入波澜。大故嗟惜者云。溺水之鬼。苦要引人。物情固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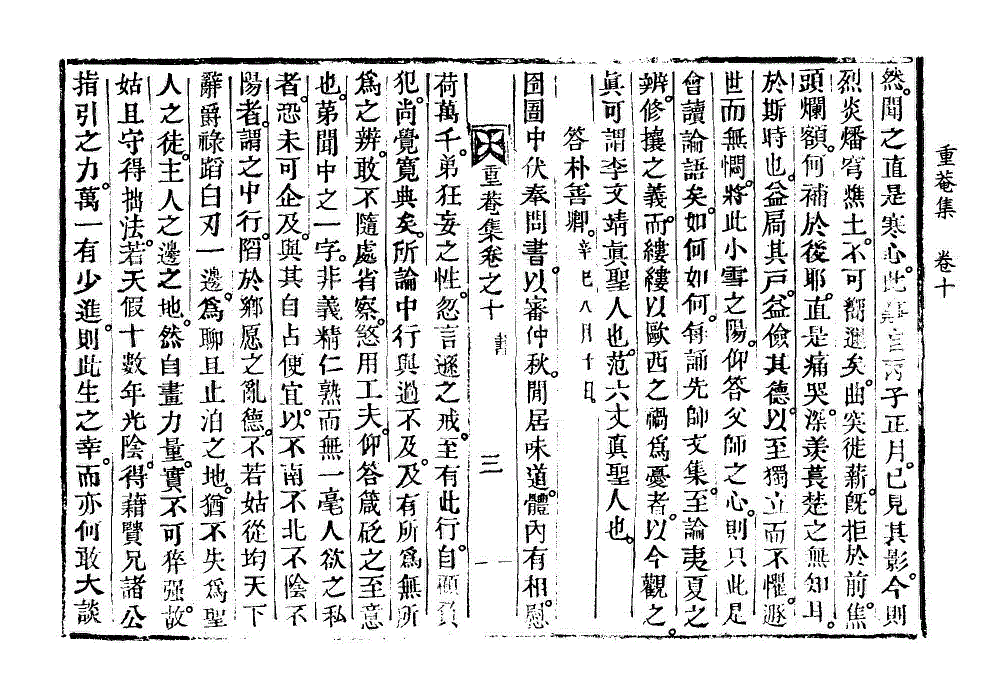 然。闻之直是寒心。此事自丙子正月。已见其影。今则烈炎燔穹燋土。不可向迩矣。曲突徙薪。既拒于前。焦头烂额。何补于后耶。直是痛哭。深羡苌楚之无知耳。于斯时也。益扃其户。益俭其德。以至独立而不惧。遁世而无悯。将此小雪之阳。仰答父师之心。则只此是会读论语矣。如何如何。每诵先师文集。至论夷夏之辨。修攘之义。而缕缕以欧西之祸为忧者。以今观之。真可谓李文靖真圣人也。范六丈真圣人也。
然。闻之直是寒心。此事自丙子正月。已见其影。今则烈炎燔穹燋土。不可向迩矣。曲突徙薪。既拒于前。焦头烂额。何补于后耶。直是痛哭。深羡苌楚之无知耳。于斯时也。益扃其户。益俭其德。以至独立而不惧。遁世而无悯。将此小雪之阳。仰答父师之心。则只此是会读论语矣。如何如何。每诵先师文集。至论夷夏之辨。修攘之义。而缕缕以欧西之祸为忧者。以今观之。真可谓李文靖真圣人也。范六丈真圣人也。答朴善卿。(辛巳八月十日。)
囹圄中伏奉问书。以审仲秋。閒居味道。体内有相。慰荷万千。弟狂妄之性。忽言逊之戒。至有此行。自顾负犯。尚觉宽典矣。所论中行与过不及。及有所为无所为之辨。敢不随处省察。煞用工夫。仰答箴砭之至意也。第闻中之一字。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恐未可企及。与其自占便宜。以不南不北不阴不阳者。谓之中行。陷于乡愿之乱德。不若姑从均天下辞爵禄蹈白刃一边。为聊且止泊之地。犹不失为圣人之徒。主人之边之地。然自画力量。实不可猝强。故姑且守得拙法。若天假十数年光阴。得藉贤兄诸公指引之力。万一有少进。则此生之幸。而亦何敢大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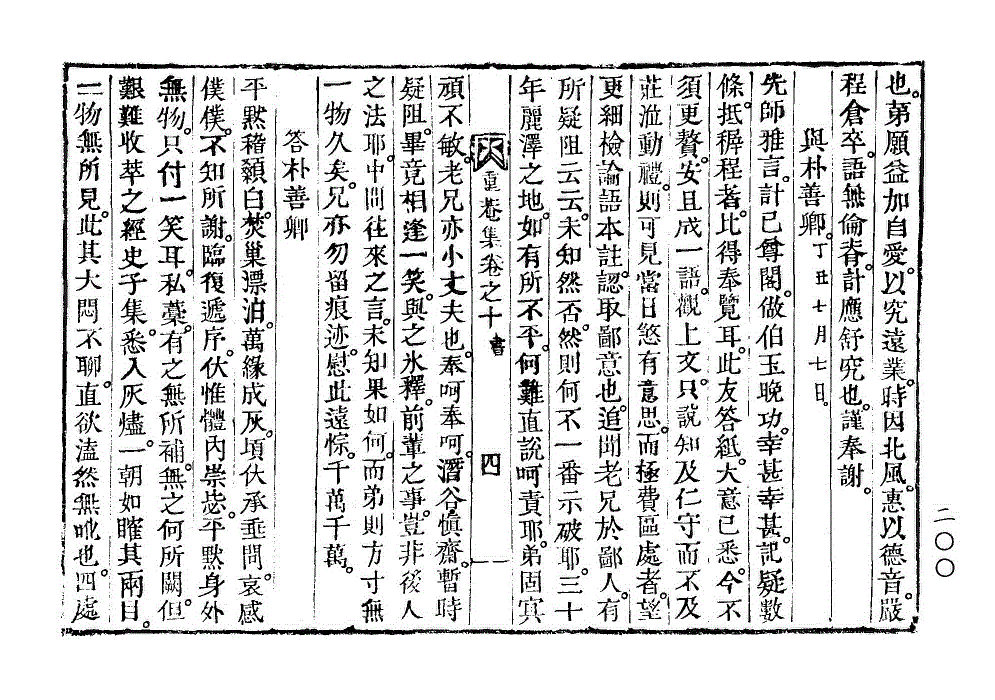 也。第愿益加自爱。以究远业。时因化风。惠以德音。严程仓卒。语无伦脊。计应舒究也。谨奉谢。
也。第愿益加自爱。以究远业。时因化风。惠以德音。严程仓卒。语无伦脊。计应舒究也。谨奉谢。与朴善卿。(丁丑七月七日。)
先师雅言。计已尊阁。做伯玉晚功。幸甚幸甚。记疑数条。抵稚程者。比得奉览耳。此友答纸。大意已悉。今不须更赘。安且成一语。观上文。只说知及仁守而不及庄涖动礼。则可见当日煞有意思。而极费区处者。望更细检论语本注。认取鄙意也。追闻老兄于鄙人。有所疑阻云云。未知然否。然则何不一番示破耶。三十年丽泽之地。如有所不平。何难直说呵责耶。弟固冥顽不敏。老兄亦小丈夫也。奉呵奉呵。潜谷,慎斋。暂时疑阻。毕竟相逢一笑。与之冰释。前辈之事。岂非后人之法耶。中间往来之言。未知果如何。而弟则方寸无一物久矣。兄亦勿留痕迹。慰此远悰。千万千万。
答朴善卿
平默稽颡白。焚巢漂泊。万缘成灰。顷伏承垂问。哀感仆仆。不知所谢。临复递序。伏惟体内崇毖。平默身外无物。只付一笑耳。私藁。有之无所补。无之何所阙。但艰难收萃之经史子集。悉入灰烬。一朝如𥉑其两目。二物无所见。此其大闷不聊。直欲溘然无吪也。四处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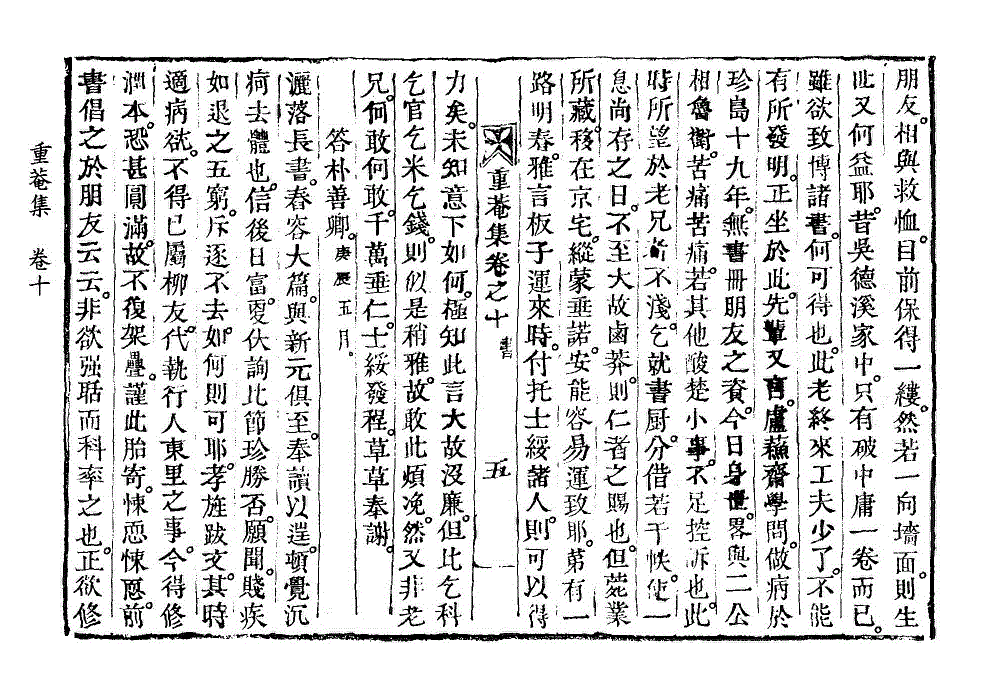 朋友。相与救恤。目前保得一缕。然若一向墙面。则生世又何益耶。昔吴德溪家中。只有破中庸一卷而已。虽欲致博诸书。何可得也。此老终来工夫少了。不能有所发明。正坐于此。先辈又言。卢苏斋学问。做病于珍岛十九年。无书册明友之资。今日身世。略与二公相鲁卫。苦痛苦痛。若其他酸楚小事。不足控诉也。此时所望于老兄者不浅。乞就书厨。分借若干帙。使一息尚存之日。不至大故卤莽。则仁者之赐也。但菀业所藏。移在京宅。纵蒙垂诺。安能容易运致耶。第有一路明春。雅言板子运来时。付托士绥诸人。则可以得力矣。未知意下如何。极知此言大故没廉。但比乞科乞官乞米乞钱。则似是稍雅。故敢此烦浼。然又非老兄。何敢何敢。千万垂仁。士绥发程。草草奉谢。
朋友。相与救恤。目前保得一缕。然若一向墙面。则生世又何益耶。昔吴德溪家中。只有破中庸一卷而已。虽欲致博诸书。何可得也。此老终来工夫少了。不能有所发明。正坐于此。先辈又言。卢苏斋学问。做病于珍岛十九年。无书册明友之资。今日身世。略与二公相鲁卫。苦痛苦痛。若其他酸楚小事。不足控诉也。此时所望于老兄者不浅。乞就书厨。分借若干帙。使一息尚存之日。不至大故卤莽。则仁者之赐也。但菀业所藏。移在京宅。纵蒙垂诺。安能容易运致耶。第有一路明春。雅言板子运来时。付托士绥诸人。则可以得力矣。未知意下如何。极知此言大故没廉。但比乞科乞官乞米乞钱。则似是稍雅。故敢此烦浼。然又非老兄。何敢何敢。千万垂仁。士绥发程。草草奉谢。答朴善卿。(庚辰五月。)
洒落长书。舂容大篇。与新元俱至。奉读以𨓏。顿觉沉疴去体也。信后日富。更伏询比节珍胜否。愿闻。贱疾如退之五穷。斥逐不去。如何则可耶。孝旌跋文。其时适病㞃。不得已属柳友。代执行人东里之事。今得修润本。恐甚圆满。故不复架叠。谨此胎寄。悚恧悚恧。前书倡之于朋友云云。非欲强聒而科率之也。正欲修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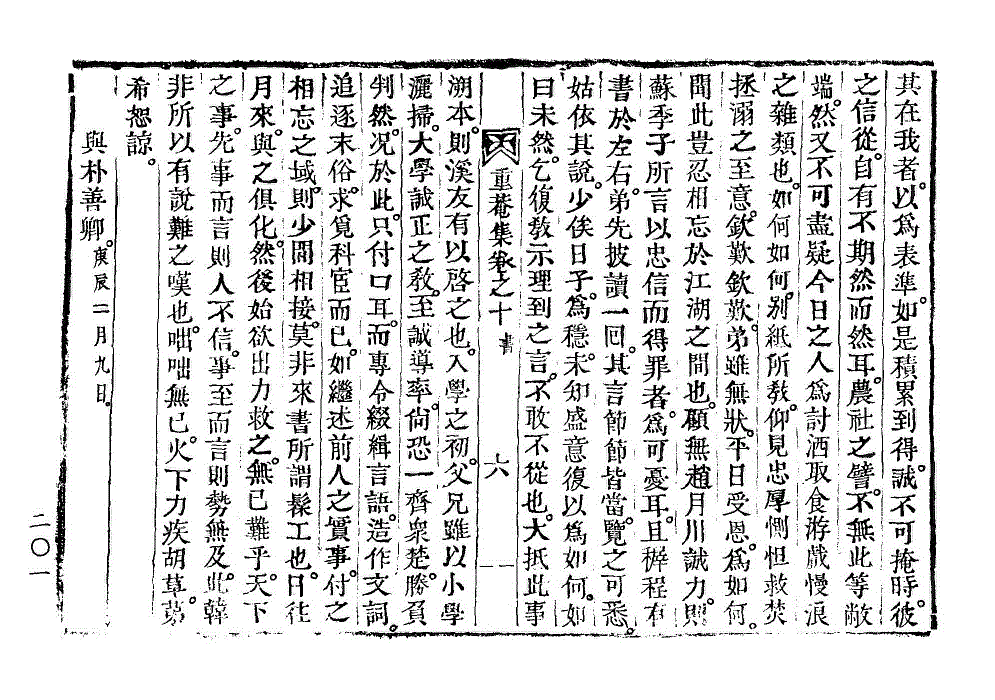 其在我者。以为表准。如是积累到得。诚不可掩时。彼之信从。自有不期然而然耳。农社之譬。不无此等敝端。然又不可尽疑今日之人为讨洒取食游戏慢浪之杂类也。如何如何。别纸所教。仰见忠厚恻怛救焚拯溺之至意。钦叹钦叹。弟虽无状。平日受恩。为如何。闻此岂忍相忘于江湖之间也。顾无赵月川诚力。则苏季子所言以忠信而得罪者。为可忧耳。且稚程有书于左右。弟先披读一回。其言节节皆当。览之可悉。姑依其说。少俟日子。为稳。未知盛意复以为如何。如曰未然。乞复教示理到之言。不敢不从也。大抵此事溯本。则溪友有以启之也。入学之初。父兄虽以小学洒扫。大学诚正之教。至诚导率。尚恐一齐众楚。胜负判然。况于此。只付口耳。而专令缀缉言语。造作文词。追逐末俗。求觅科宦而已。如继述前人之实事。付之相忘之域。则少间相接。莫非来书所谓髹工也。日往月来。与之俱化。然后始欲出力救之。无已难乎。天下之事。先事而言则人不信。事至而言则势无及。此韩非所以有说难之叹也。咄咄无已。火下力疾胡草。第希恕谅。
其在我者。以为表准。如是积累到得。诚不可掩时。彼之信从。自有不期然而然耳。农社之譬。不无此等敝端。然又不可尽疑今日之人为讨洒取食游戏慢浪之杂类也。如何如何。别纸所教。仰见忠厚恻怛救焚拯溺之至意。钦叹钦叹。弟虽无状。平日受恩。为如何。闻此岂忍相忘于江湖之间也。顾无赵月川诚力。则苏季子所言以忠信而得罪者。为可忧耳。且稚程有书于左右。弟先披读一回。其言节节皆当。览之可悉。姑依其说。少俟日子。为稳。未知盛意复以为如何。如曰未然。乞复教示理到之言。不敢不从也。大抵此事溯本。则溪友有以启之也。入学之初。父兄虽以小学洒扫。大学诚正之教。至诚导率。尚恐一齐众楚。胜负判然。况于此。只付口耳。而专令缀缉言语。造作文词。追逐末俗。求觅科宦而已。如继述前人之实事。付之相忘之域。则少间相接。莫非来书所谓髹工也。日往月来。与之俱化。然后始欲出力救之。无已难乎。天下之事。先事而言则人不信。事至而言则势无及。此韩非所以有说难之叹也。咄咄无已。火下力疾胡草。第希恕谅。与朴善卿。(庚辰二月九日。)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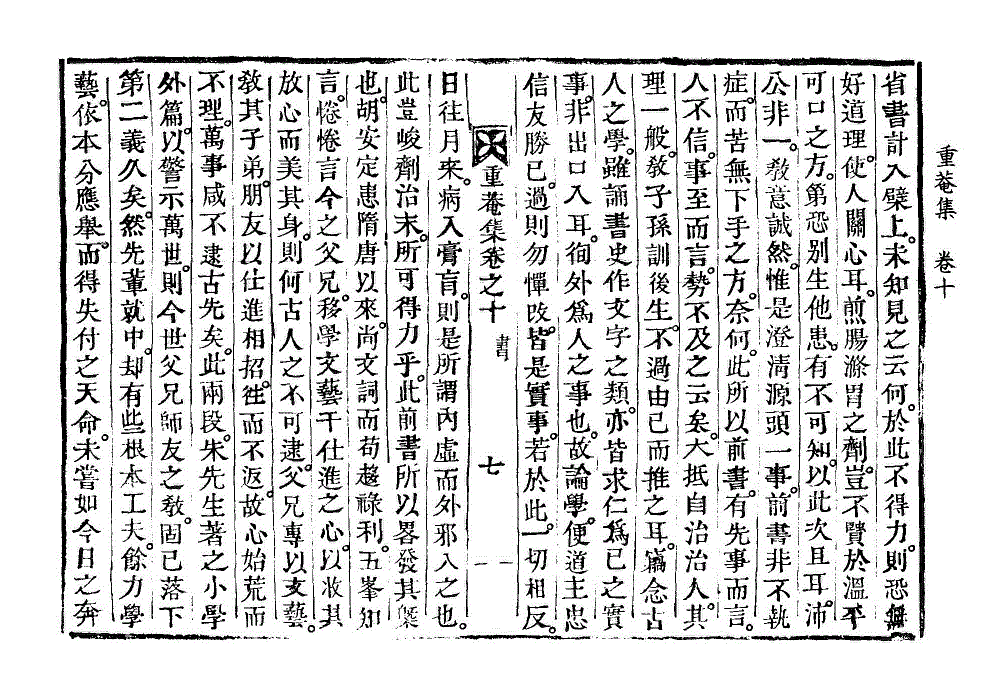 省书计入檗上。未知见之云何。于此不得力。则恐无好道理。使人关心耳。煎肠涤胃之剂。岂不贤于温平可口之方。第恐别生他患。有不可知。以此次且耳。沛公非一。教意诚然。惟是澄清源头一事。前书非不执症。而苦无下手之方。奈何。此所以前书。有先事而言。人不信。事至而言。势不及之云矣。大抵自治治人。其理一般。教子孙训后生。不过由己而推之耳。窃念古人之学。虽诵书史作文字之类。亦皆求仁为己之实事。非出口入耳。徇外为人之事也。故论学。便道主忠信友胜己。过则勿惮改。皆是实事。若于此。一切相反。日往月来。病入膏肓。则是所谓内虚而外邪入之也。此岂峻剂治末。所可得力乎。此前书所以略发其槩也。胡安定患隋唐以来。尚文词而苟趍禄利。五峰知言。惓惓言今之父兄。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则何古人之不可逮。父兄专以文艺。教其子弟。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返。故心始荒而不理。万事咸不逮古先矣。此两段。朱先生著之小学外篇。以警示万世。则今世父兄师友之教。固已落下第二义久矣。然先辈就中。却有些根本工夫。馀力学艺。依本分应举。而得失付之天命。未尝如今日之奔
省书计入檗上。未知见之云何。于此不得力。则恐无好道理。使人关心耳。煎肠涤胃之剂。岂不贤于温平可口之方。第恐别生他患。有不可知。以此次且耳。沛公非一。教意诚然。惟是澄清源头一事。前书非不执症。而苦无下手之方。奈何。此所以前书。有先事而言。人不信。事至而言。势不及之云矣。大抵自治治人。其理一般。教子孙训后生。不过由己而推之耳。窃念古人之学。虽诵书史作文字之类。亦皆求仁为己之实事。非出口入耳。徇外为人之事也。故论学。便道主忠信友胜己。过则勿惮改。皆是实事。若于此。一切相反。日往月来。病入膏肓。则是所谓内虚而外邪入之也。此岂峻剂治末。所可得力乎。此前书所以略发其槩也。胡安定患隋唐以来。尚文词而苟趍禄利。五峰知言。惓惓言今之父兄。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则何古人之不可逮。父兄专以文艺。教其子弟。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返。故心始荒而不理。万事咸不逮古先矣。此两段。朱先生著之小学外篇。以警示万世。则今世父兄师友之教。固已落下第二义久矣。然先辈就中。却有些根本工夫。馀力学艺。依本分应举。而得失付之天命。未尝如今日之奔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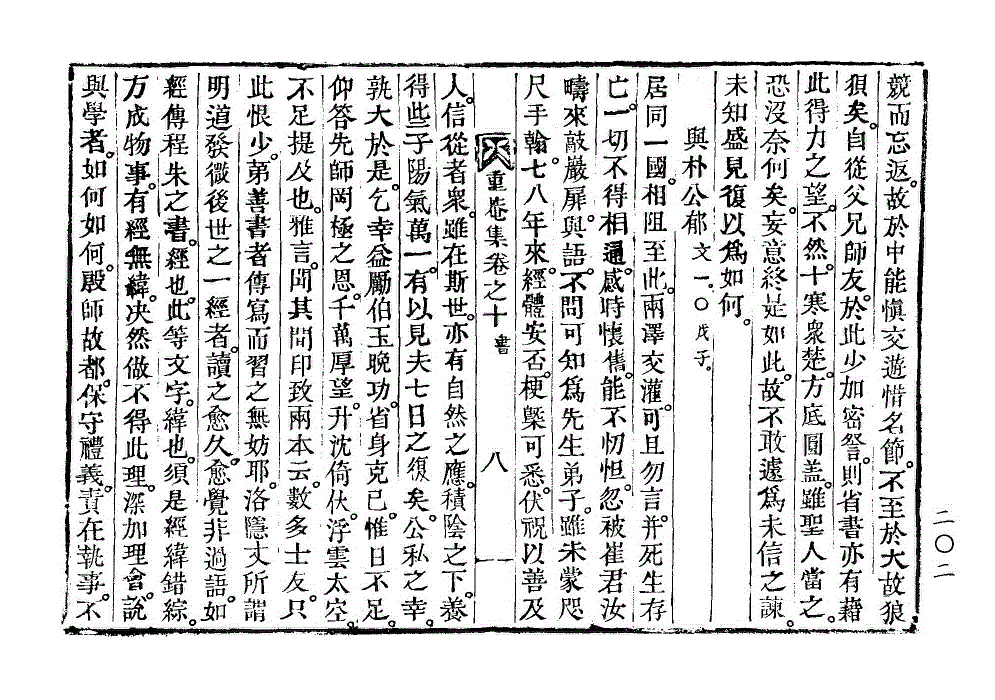 竞而忘返。故于中能慎交游惜名节。不至于大故狼狈矣。自从父兄师友。于此少加密察。则省书亦有藉此得力之望。不然。十寒众楚。方底圆盖。虽圣人当之。恐没奈何矣。妄意终是如此。故不敢遽为未信之谏。未知盛见复以为如何。
竞而忘返。故于中能慎交游惜名节。不至于大故狼狈矣。自从父兄师友。于此少加密察。则省书亦有藉此得力之望。不然。十寒众楚。方底圆盖。虽圣人当之。恐没奈何矣。妄意终是如此。故不敢遽为未信之谏。未知盛见复以为如何。与朴公郁(文一。○戊子。)
居同一国。相阻至此。两泽交灌。可且勿言。并死生存亡。一切不得相通。感时怀旧。能不忉怛。忽被崔君汝畴来敲岩扉。与语。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虽未蒙咫尺手翰。七八年来。经体安否。梗槩可悉。伏祝以善及人。信从者众。虽在斯世。亦有自然之应。积阴之下。养得些子阳气万一。有以见夫七日之复矣。公私之幸。孰大于是。乞幸益励伯玉晚功。省身克己。惟日不足。仰答先师冈极之恩。千万厚望。升沈倚伏。浮云太空。不足提及也。雅言。闻其间印致两本云。数多士友。只此恨少。第善书者传写而习之无妨耶。洛隐丈所谓明道发微后世之一经者。读之愈久。愈觉非过语。如经传程朱之书。经也。此等文字。纬也。须是经纬错综。方成物事。有经无纬。决然做不得此理。深加理会。说与学者。如何如何。殷师故都。保守礼义。责在执事。不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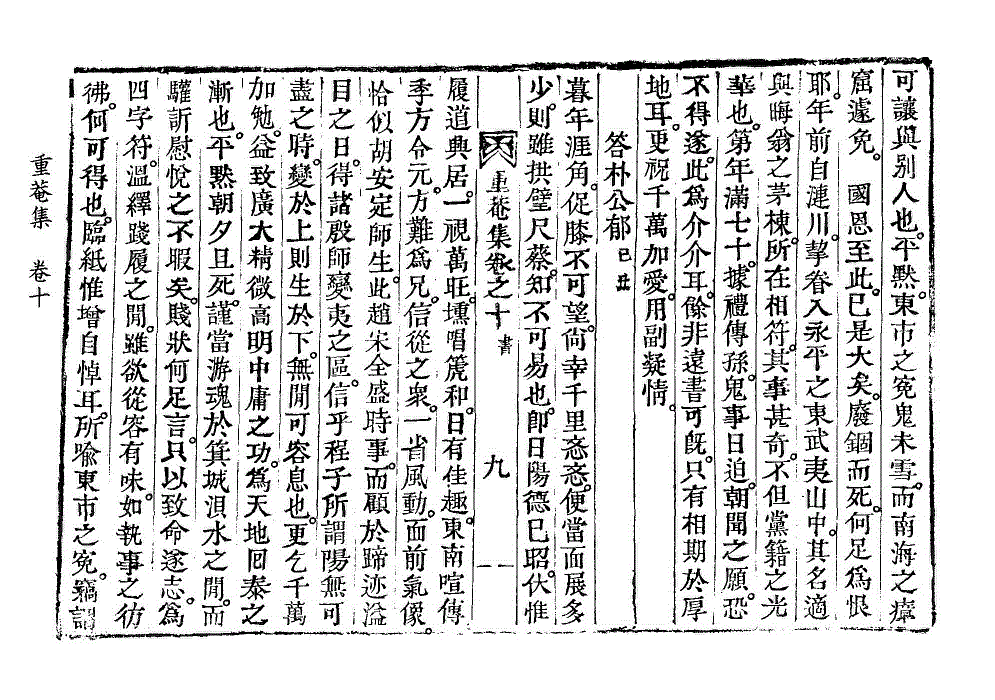 可让与别人也。平默。东市之冤鬼未雪。而南海之瘴窟遽免。 国恩至此。已是大矣。废锢而死。何足为恨耶。年前自涟川。挈眷入永平之东武夷山中。其名适与晦翁之茅栋。所在相符。其事甚奇。不但党籍之光华也。第年满七十。据礼传孙。鬼事日迫。朝闻之愿。恐不得遂。此为介介耳。馀非远书可既。只有相期于厚地耳。更祝千万加爱。用副凝情。
可让与别人也。平默。东市之冤鬼未雪。而南海之瘴窟遽免。 国恩至此。已是大矣。废锢而死。何足为恨耶。年前自涟川。挈眷入永平之东武夷山中。其名适与晦翁之茅栋。所在相符。其事甚奇。不但党籍之光华也。第年满七十。据礼传孙。鬼事日迫。朝闻之愿。恐不得遂。此为介介耳。馀非远书可既。只有相期于厚地耳。更祝千万加爱。用副凝情。答朴公郁(己丑)
暮年涯角。促膝不可望。尚幸千里忞忞。便当面展多少。则虽拱璧尺蔡。知不可易也。即日阳德已昭。伏惟履道兴居。一视万旺。埙唱篪和。日有佳趣。东南喧传季方令元。方难为兄。信从之众。一省风动。面前气像。恰似胡安定师生。此赵宋全盛时事。而顾于蹄迹溢目之日。得诸殷师变夷之区。信乎程子所谓阳无可尽之时。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閒可容息也。更乞千万加勉。益致广大精微高明中庸之功。为天地回泰之渐也。平默朝夕且死。谨当游魂于箕城浿水之閒。而驩䜣慰悦之不暇矣。贱状何足言。只以致命遂志。为四字符。温绎践履之閒。虽欲从容有味。如执事之彷佛。何可得也。临纸惟增自悼耳。所喻东市之冤。窃谓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3L 页
 非干一人一家之私。乃是龙血玄黄之惨。而首尾十年。田夫野老街童走卒。一齐扼腕而不之闻耳。但今好恶向背。恐未有伸雪之期。少俟何益耶。俯仰长吁。不如无聪也。珍函出于孟陬者。数日前。方始承拜。今日出付者。又不知何日入彻也。幸不至浮沉耶。只祝加护经体。慰此溯用。
非干一人一家之私。乃是龙血玄黄之惨。而首尾十年。田夫野老街童走卒。一齐扼腕而不之闻耳。但今好恶向背。恐未有伸雪之期。少俟何益耶。俯仰长吁。不如无聪也。珍函出于孟陬者。数日前。方始承拜。今日出付者。又不知何日入彻也。幸不至浮沉耶。只祝加护经体。慰此溯用。答李秀直(浩。○丁丑五月。)
隔江相望。只切溯用。伏蒙翰寄。谨悉旅安。慰何可言。平默衰颓之相。日甚一日。无可奈何。麦粮径尽。自秋耕时。已料其然。皆任之而已。学道不成迂拙狂妄之一弃物。病死饿死。何足嘅惜为也。下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如殷人当服殷先王所定之服。周人当从周先王所定之服。若殷人从夏后之服。周人从殷王之制。及如郑子臧鹬冠之类。则非所谓服先王之法服也。先王之法言。如尧舜典谟。三王诰命之类。其言可为万世法程者也。先王之德行。即本之身心性情。行之人伦日用礼乐文章政事钜细精粗。泛应而曲当者皆是也。府兵。如唐时分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七十一。皆隶十二卫。凡府有三等。上等兵一千二百人。中等千人。下等八百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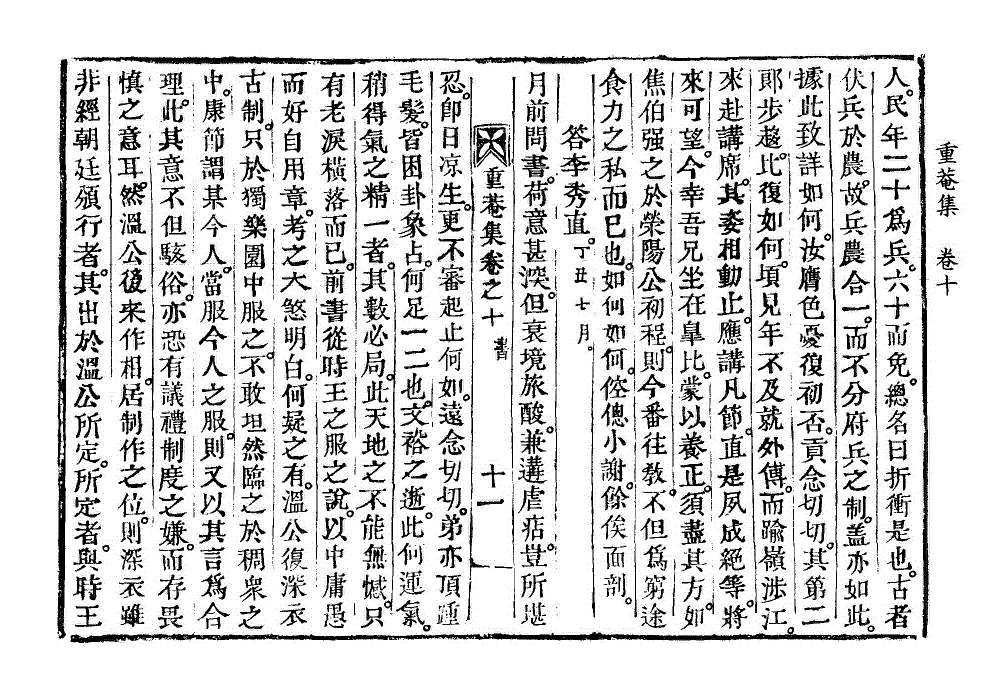 人。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总名曰折冲是也。古者伏兵于农。故兵农合一。而不分府兵之制。盖亦如此。据此致详如何。汝膺色忧复初否。贡念切切。其第二郎步趍。比复如何。顷见年不及就外传。而踰岭涉江。来赴讲席。其姿相动止。应讲凡节。直是夙成绝等。将来可望。今幸吾兄坐在皋比。蒙以养正。须尽其方。如焦伯强之于荥阳公初程。则今番往教。不但为穷途食力之私而已也。如何如何。倥偬小谢。馀俟面剖。
人。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总名曰折冲是也。古者伏兵于农。故兵农合一。而不分府兵之制。盖亦如此。据此致详如何。汝膺色忧复初否。贡念切切。其第二郎步趍。比复如何。顷见年不及就外传。而踰岭涉江。来赴讲席。其姿相动止。应讲凡节。直是夙成绝等。将来可望。今幸吾兄坐在皋比。蒙以养正。须尽其方。如焦伯强之于荥阳公初程。则今番往教。不但为穷途食力之私而已也。如何如何。倥偬小谢。馀俟面剖。答李秀直。(丁丑七月。)
月前问书。荷意甚深。但衰境旅酸。兼遘虐痁。岂所堪忍。即日凉生。更不审起止何如。远念切切。弟亦顶踵毛发。皆困卦象占。何足一二也。文裕之逝。此何运气。稍得气之精一者。其数必局。此天地之不能无憾。只有老泪横落而已。前书从时王之服之说。以中庸愚而好自用章。考之大煞明白。何疑之有。温公复深衣古制。只于独乐园中服之。不敢坦然临之于稠众之中。康节谓某今人。当服今人之服。则又以其言为合理。此其意不但骇俗。亦恐有议礼制度之嫌。而存畏慎之意耳。然温公后来作相。居制作之位。则深衣虽非经朝廷颁行者。其出于温公所定。所定者。与时王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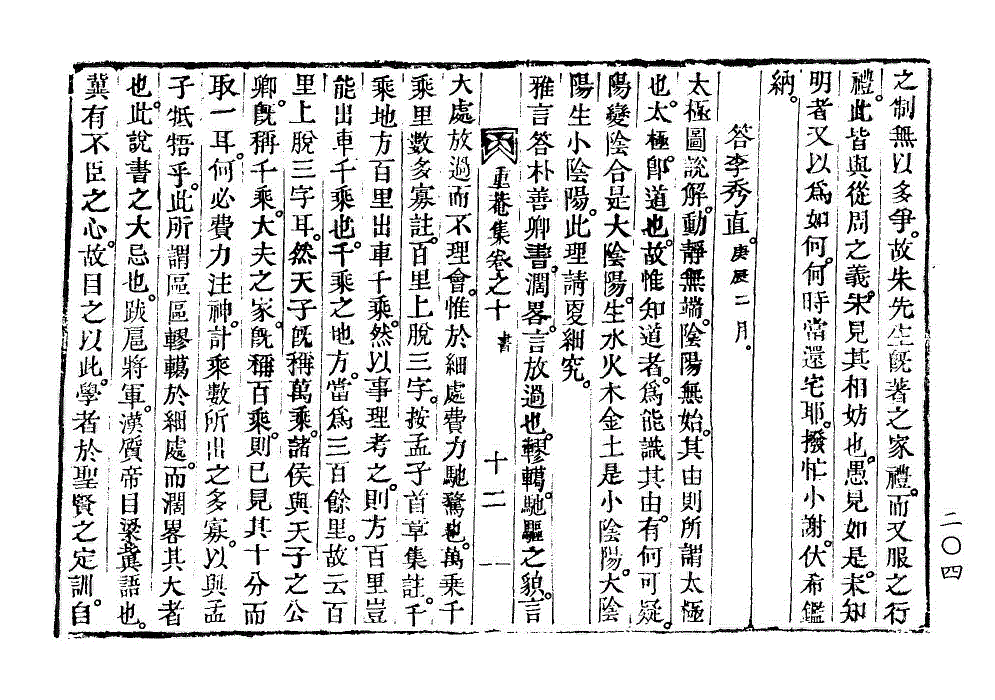 之制无以多争。故朱先生既著之家礼。而又服之行礼。此皆与从周之义。未见其相妨也。愚见如是。未知明者又以为如何。何时当还宅耶。拨忙小谢。伏希鉴纳。
之制无以多争。故朱先生既著之家礼。而又服之行礼。此皆与从周之义。未见其相妨也。愚见如是。未知明者又以为如何。何时当还宅耶。拨忙小谢。伏希鉴纳。答李秀直。(庚辰二月。)
太极图说解。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其由则所谓太极也。太极。即道也。故惟知道者。为能识其由。有何可疑。阳变阴合是大阴阳。生水火木金土是小阴阳。大阴阳生小阴阳。此理请更细究。
雅言答朴善卿书。阔略。言放过也。轇轕。驰驱之貌。言大处放过而不理会。惟于细处费力驰骛也。万乘千乘里数多寡注。百里上脱三字。按孟子首章集注。千乘地方百里出车千乘。然以事理考之。则方百里岂能出车千乘也。千乘之地方。当为三百馀里。故云百里上脱三字耳。然天子既称万乘。诸侯与天子之公卿。既称千乘。大夫之家。既称百乘。则已见其十分而取一耳。何必费力注神。计乘数所出之多寡。以与孟子牴牾乎。此所谓区区轇轕于细处。而阔略其大者也。此说书之大忌也。跋扈将军。汉质帝目梁冀语也。冀有不臣之心。故目之以此。学者于圣贤之定训。自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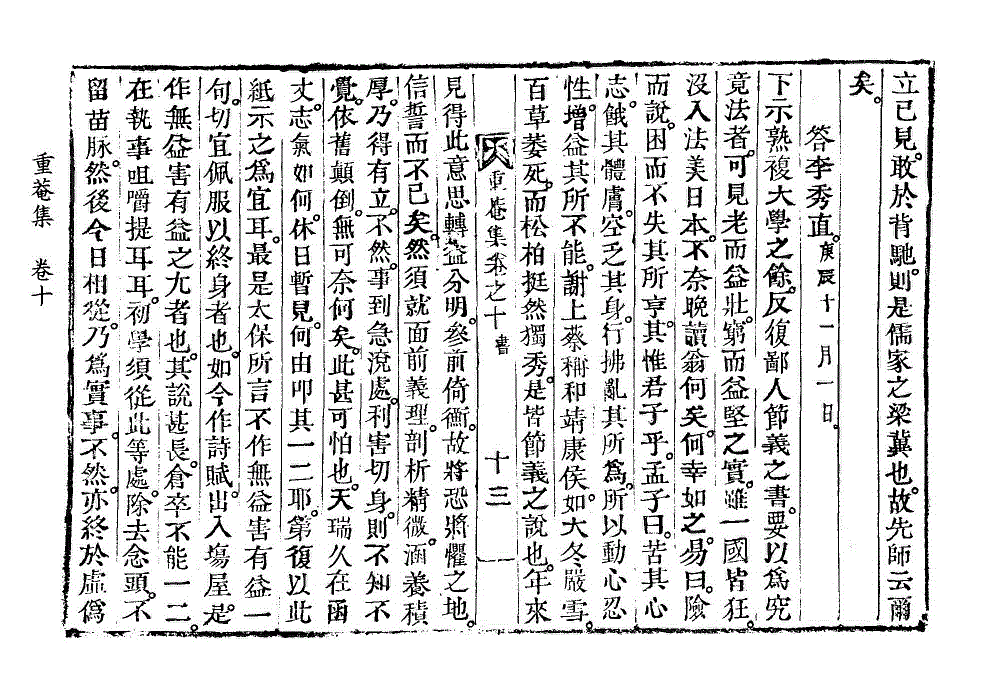 立己见。敢于背驰。则是儒家之梁冀也。故先师云尔矣。
立己见。敢于背驰。则是儒家之梁冀也。故先师云尔矣。答李秀直。(庚辰十一月一日。)
下示熟复大学之馀。反复鄙人节义之书。要以为究竟法者。可见老而益壮。穷而益坚之实。虽一国皆狂。没入法美日本。不奈晚读翁何矣。何幸如之。易曰。险而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孟子曰。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谢上蔡称和靖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是皆节义之说也。年来见得此意思转益分明。参前倚衡。故将恐将惧之地。信誓而不已矣。然须就面前义理。剖析精微。涵养积厚。乃得有立。不然。事到急渷处。利害切身。则不知不觉。依旧颠倒。无可奈何矣。此甚可怕也。天瑞久在函丈。志气如何。休日暂见。何由叩其一二耶。第复以此纸示之为宜耳。最是太保所言不作无益害有益一句。切宜佩服以终身者也。如今作诗赋。出入场屋。是作无益害有益之尤者也。其说甚长。仓卒不能一二。在执事咀嚼提耳耳。初学须从此等处。除去念头。不留苗脉。然后今日相从。乃为实事。不然。亦终于虚伪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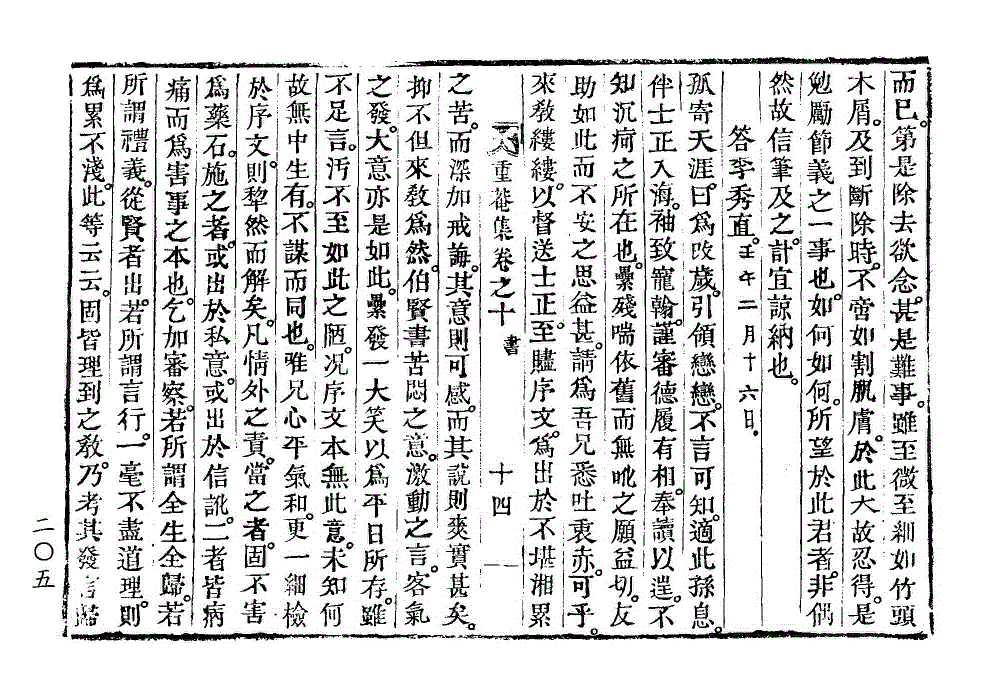 而已。第是除去欲念。甚是难事。虽至微至细如竹头木屑。及到断除时。不啻如割肌肤。于此大故忍得。是勉励节义之一事也。如何如何。所望于此君者。非偶然故信笔及之。计宜谅纳也。
而已。第是除去欲念。甚是难事。虽至微至细如竹头木屑。及到断除时。不啻如割肌肤。于此大故忍得。是勉励节义之一事也。如何如何。所望于此君者。非偶然故信笔及之。计宜谅纳也。答李秀直。(壬午二月十六日。)
孤寄天涯。曰为改岁。引领恋恋。不言可知。适此孙息。伴士正入海。袖致宠翰。谨审德履有相。奉读以𨓏。不知沉疴之所在也。累残喘依旧而无吪之愿益切。友助如此而不安之思益甚。请为吾兄悉吐衷赤。可乎。来教缕缕。以督送士正。至赆序文。为出于不堪湘累之苦。而深加戒诲。其意则可感。而其说则爽实甚矣。抑不但来教为然。伯贤书苦闷之意。激动之言。客气之发。大意亦是如此。累发一大笑以为平日所存。虽不足言。污不至如此之陋。况序文本无此意。未知何故无中生有。不谋而同也。唯兄心平气和。更一细检于序文。则犁然而解矣。凡情外之责。当之者。固不害为药石。施之者。或出于私意。或出于信讹。二者皆病痛而为害事之本也。乞加审察。若所谓全生全归。若所谓礼义。从贤者出。若所谓言行。一毫不尽道理。则为累不浅。此等云云。固皆理到之教。乃考其发言归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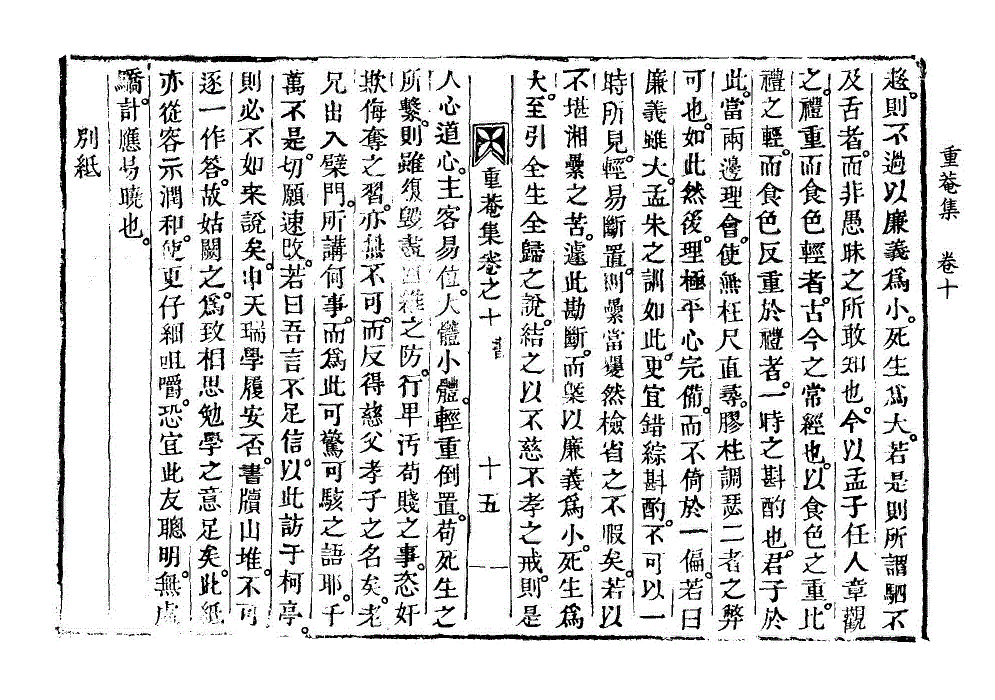 趍。则不过以廉义为小。死生为大。若是则所谓驷不及舌者。而非愚昧之所敢知也。今以孟子任人章观之。礼重而食色轻者。古今之常经也。以食色之重。比礼之轻。而食色反重于礼者。一时之斟酌也。君子于此。当两边理会。使无枉尺直寻。胶柱调瑟二者之弊可也。如此然后。理极平心完备。而不倚于一偏。若曰廉义虽大。孟朱之训如此。更宜错综斟酌。不可以一时所见。轻易断置。则累当矍然检省之不暇矣。若以不堪湘累之苦。遽此勘断。而槩以廉义为小。死生为大。至弓全生全归之说。结之以不慈不孝之戒。则是人心道心。主客易位。大体小体。轻重倒置。苟死生之所系。则虽复毁尽四维之防。行卑污苟贱之事。恣奸欺侮夺之习。亦无不可。而反得慈父孝子之名矣。老兄出入檗门。所讲何事。而为此可惊可骇之语耶。千万不是。切愿速改。若曰吾言不足信。以此访于柯亭。则必不如来说矣。申天瑞学履安否。书牍山堆。不可逐一作答。故姑阙之。为致相思勉学之意足矣。此纸亦从容示润和。使更仔细咀嚼。恐宜此友聪明。无虑骄。计应易晓也。
趍。则不过以廉义为小。死生为大。若是则所谓驷不及舌者。而非愚昧之所敢知也。今以孟子任人章观之。礼重而食色轻者。古今之常经也。以食色之重。比礼之轻。而食色反重于礼者。一时之斟酌也。君子于此。当两边理会。使无枉尺直寻。胶柱调瑟二者之弊可也。如此然后。理极平心完备。而不倚于一偏。若曰廉义虽大。孟朱之训如此。更宜错综斟酌。不可以一时所见。轻易断置。则累当矍然检省之不暇矣。若以不堪湘累之苦。遽此勘断。而槩以廉义为小。死生为大。至弓全生全归之说。结之以不慈不孝之戒。则是人心道心。主客易位。大体小体。轻重倒置。苟死生之所系。则虽复毁尽四维之防。行卑污苟贱之事。恣奸欺侮夺之习。亦无不可。而反得慈父孝子之名矣。老兄出入檗门。所讲何事。而为此可惊可骇之语耶。千万不是。切愿速改。若曰吾言不足信。以此访于柯亭。则必不如来说矣。申天瑞学履安否。书牍山堆。不可逐一作答。故姑阙之。为致相思勉学之意足矣。此纸亦从容示润和。使更仔细咀嚼。恐宜此友聪明。无虑骄。计应易晓也。别纸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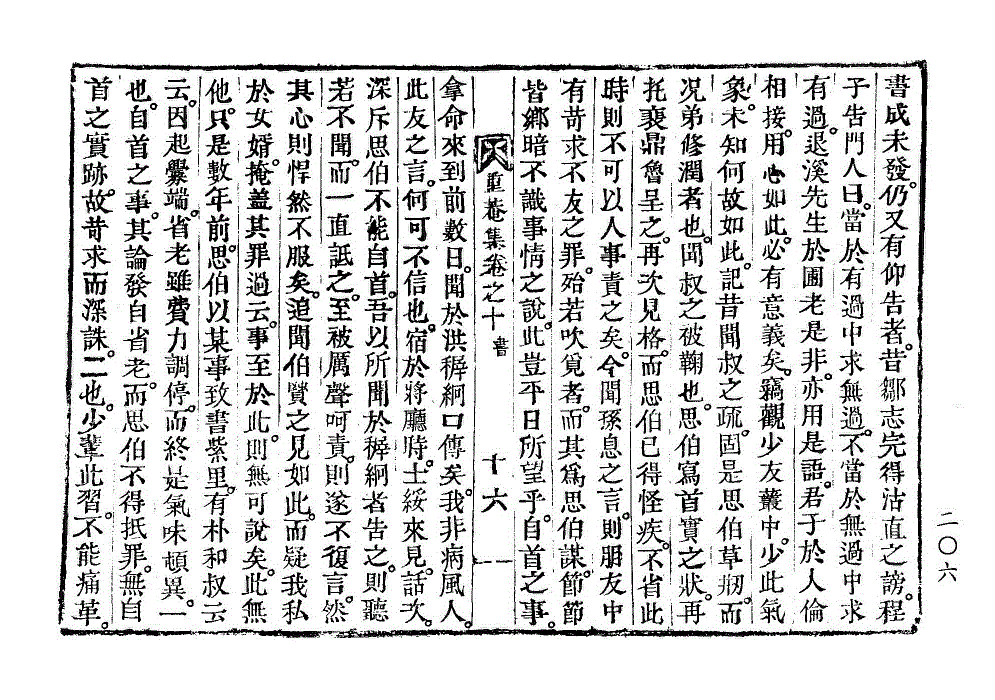 书成未发。仍又有仰告者。昔邹志完得沽直之谤。程子告门人曰。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退溪先生于圃老是非。亦用是语。君子于人伦相接。用心如此。必有意义矣。窃观少友䕺中。少此气象。未知何故如此。记昔闻叔之疏。固是思伯草刱。而况弟修润者也。闻叔之被鞠也。思伯写首实之状。再托裴鼎鲁呈之。再次见格。而思伯已得怪疾。不省此时则不可以人事责之矣。今闻逊息之言。则朋友中有苛求不友之罪。殆若吹觅者。而其为思伯谋。节节皆乡暗不识事情之说。此岂平日所望乎。自首之事。拿命来到前数日。闻于洪稚絅口传矣。我非病风人。此友之言。何可不信也。宿于将厅时。士绥来见。话次。深斥思伯不能自首。吾以所闻于稚絅者告之。则听若不闻。而一直诋之。至被厉声呵责。则遂不复言。然其心则悍然不服矣。追闻伯贤之见如此。而疑我私于女婿。掩盖其罪过云。事至于此。则无可说矣。此无他。只是数年前。思伯以某事致书紫里。有朴和叔云云。因起衅端。省老虽费力调停。而终是气味顿异。一也。自首之事。其论发自省老。而思伯不得抵罪。无自首之实迹。故苛求而深诛。二也。少辈此习。不能痛革。
书成未发。仍又有仰告者。昔邹志完得沽直之谤。程子告门人曰。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退溪先生于圃老是非。亦用是语。君子于人伦相接。用心如此。必有意义矣。窃观少友䕺中。少此气象。未知何故如此。记昔闻叔之疏。固是思伯草刱。而况弟修润者也。闻叔之被鞠也。思伯写首实之状。再托裴鼎鲁呈之。再次见格。而思伯已得怪疾。不省此时则不可以人事责之矣。今闻逊息之言。则朋友中有苛求不友之罪。殆若吹觅者。而其为思伯谋。节节皆乡暗不识事情之说。此岂平日所望乎。自首之事。拿命来到前数日。闻于洪稚絅口传矣。我非病风人。此友之言。何可不信也。宿于将厅时。士绥来见。话次。深斥思伯不能自首。吾以所闻于稚絅者告之。则听若不闻。而一直诋之。至被厉声呵责。则遂不复言。然其心则悍然不服矣。追闻伯贤之见如此。而疑我私于女婿。掩盖其罪过云。事至于此。则无可说矣。此无他。只是数年前。思伯以某事致书紫里。有朴和叔云云。因起衅端。省老虽费力调停。而终是气味顿异。一也。自首之事。其论发自省老。而思伯不得抵罪。无自首之实迹。故苛求而深诛。二也。少辈此习。不能痛革。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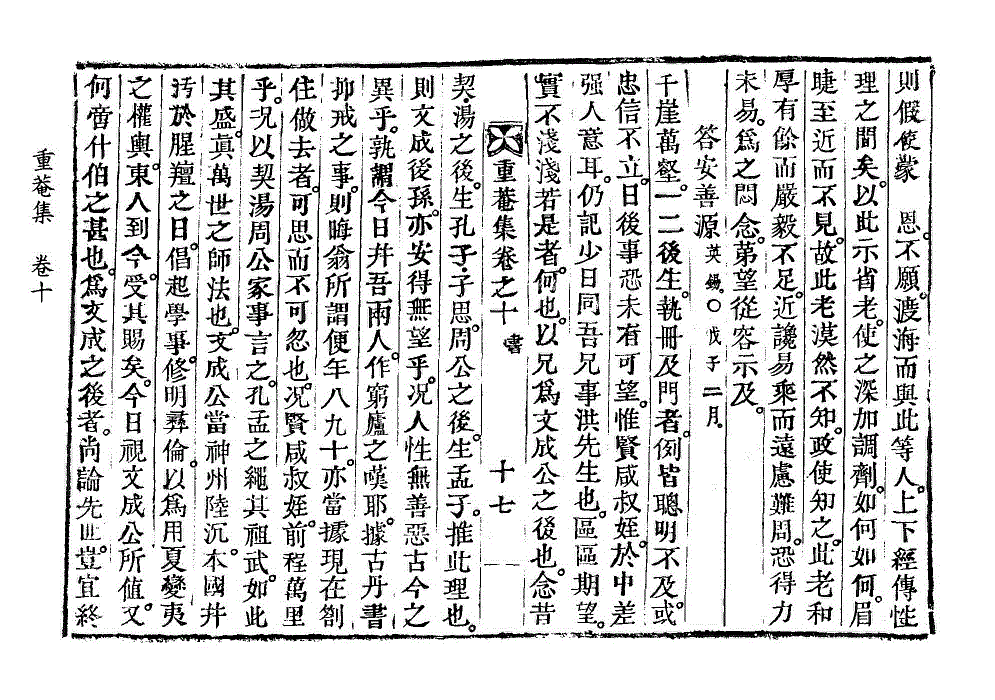 则假使蒙 恩。不愿。渡海而与此等人。上下经传性理之间矣。以此示省老。使之深加调剂。如何如何。眉睫至近而不见。故此老漠然不知。政使知之。此老和厚有馀而严毅不足。近谗易乘而远虑难周。恐得力未易。为之闷念。第望从容示及。
则假使蒙 恩。不愿。渡海而与此等人。上下经传性理之间矣。以此示省老。使之深加调剂。如何如何。眉睫至近而不见。故此老漠然不知。政使知之。此老和厚有馀而严毅不足。近谗易乘而远虑难周。恐得力未易。为之闷念。第望从容示及。答安善源(英锡。○戊子二月。)
千崖万壑。一二后生。执册及门者。例皆聪明不及。或忠信不立。日后事恐未有可望。惟贤咸叔侄。于中差强人意耳。仍记少日同吾兄事洪先生也。区区期望。实不浅浅若是者。何也。以兄为文成公之后也。念昔契,汤之后。生孔子,子思。周公之后。生孟子。推此理也。则文成后孙。亦安得无望乎。况人性无善恶古今之异乎。孰谓今日并吾两人。作穷庐之叹耶。据古丹书抑戒之事。则晦翁所谓便年八九十。亦当据现在劄住做去者。可思而不可忽也。况贤咸叔侄。前程万里乎。况以契汤周公家事言之。孔孟之绳其祖武。如此其盛。真万世之师法也。文成公当神州陆沉。本国并污于腥膻之日。倡起学事。修明彝伦。以为用夏变夷之权舆。东人到今。受其赐矣。今日视文成公所值。又何啻什伯之甚也。为文成之后者。尚论先世。岂宜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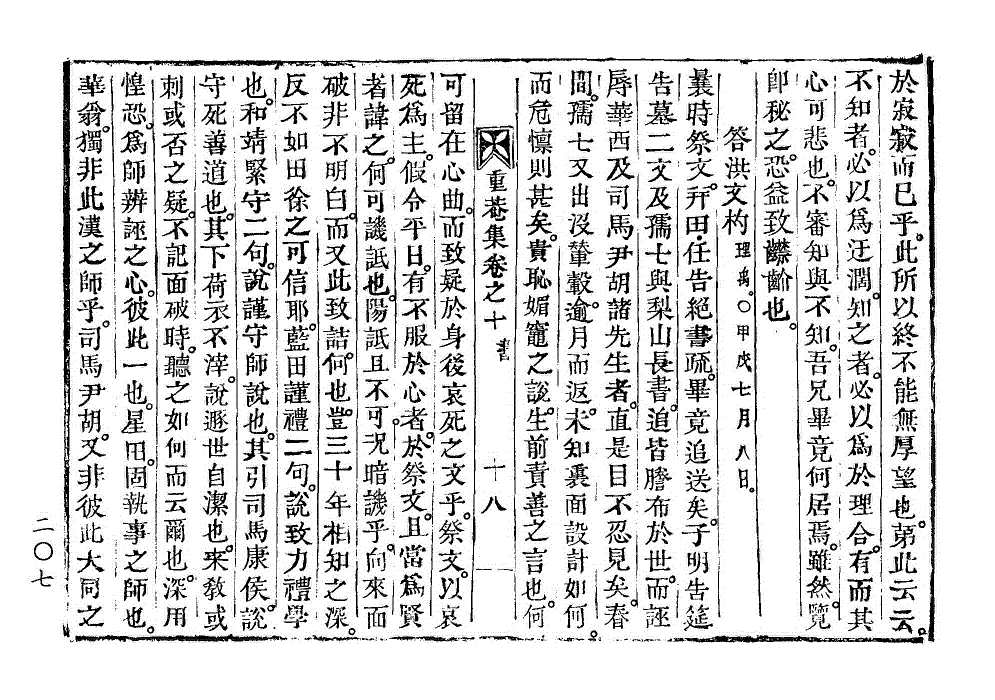 于寂寂而已乎。此所以终不能无厚望也。第此云云。不知者。必以为迂阔。知之者。必以为于理合。有而其心可悲也。不审知与不知。吾兄毕竟何居焉。虽然。览即秘之。恐益致齽齘也。
于寂寂而已乎。此所以终不能无厚望也。第此云云。不知者。必以为迂阔。知之者。必以为于理合。有而其心可悲也。不审知与不知。吾兄毕竟何居焉。虽然。览即秘之。恐益致齽齘也。答洪文杓(理禹。○甲戌七月八日。)
曩时祭文。并田,任告绝书疏。毕竟追送矣。子明告筵告墓二文及孺七与梨山长书。追皆誊布于世。而诬辱华西及司马尹胡诸先生者。直是目不忍见矣。春间。孺七又出没辇毂。逾月而返。未知里面设计如何。而危懔则甚矣。贵耻媚灶之说。生前责善之言也。何可留在心曲。而致疑于身后哀死之文乎。祭文。以哀死为主。假令平日。有不服于心者。于祭文。且当为贤者讳之。何可讥诋也。阳诋且不可。况暗讥乎。向来面破非不明白。而又此致诘。何也。岂三十年相知之深。反不如田徐之可信耶。蓝田谨礼二句。说致力礼学也。和靖紧守二句。说谨守师说也。其引司马康侯。说守死善道也。其下荷衣不滓。说遁世自洁也。来教或刺或否之疑。不记面破时。听之如何而云尔也。深用惶恐。为师辨诬之心。彼此一也。星田。固执事之师也。华翁。独非此汉之师乎。司马尹胡。又非彼此大同之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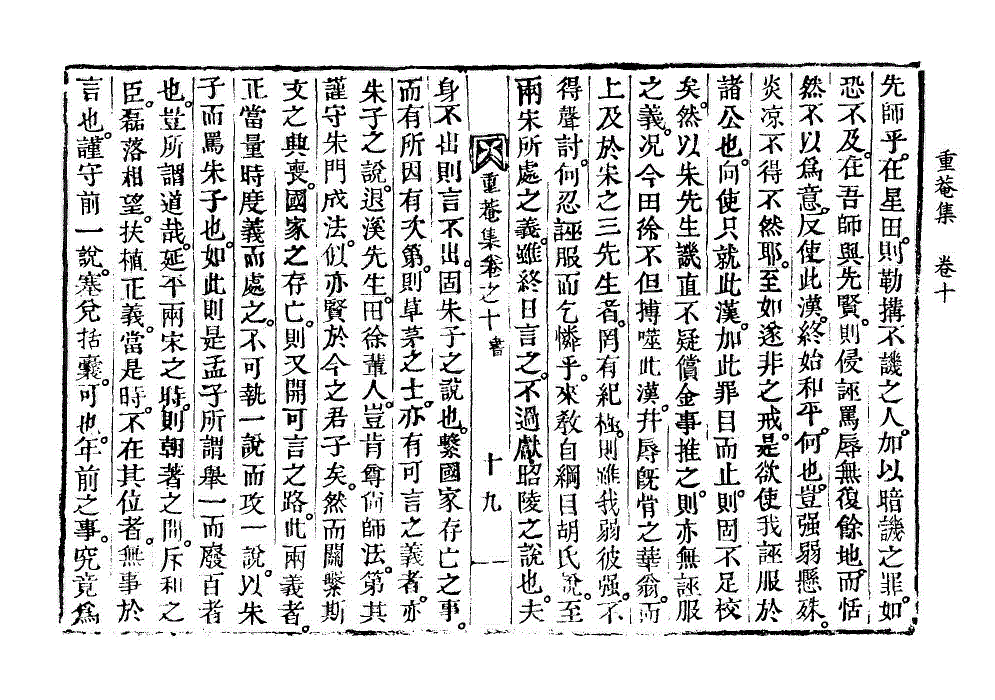 先师乎。在星田。则勒搆不讥之人。加以暗讥之罪。如恐不及。在吾师与先贤。则侵诬骂辱无复馀地而恬然不以为意。反使此汉。终始和平。何也。岂强弱悬殊。炎凉不得不然耶。至如遂非之戒。是欲使我诬服于诸公也。向使只就此汉。加此罪目而止。则固不足校矣。然以朱先生讥直不疑偿金事推之。则亦无诬服之义。况今田徐不但搏噬此汉。并辱既骨之华翁。而上及于宋之三先生者。罔有纪极。则虽我弱彼强。不得声讨。何忍诬服而乞怜乎。来教自纲目胡氏说。至两宋所处之义。虽终日言之。不过献昭陵之说也。夫身不出则言不出。固朱子之说也。系国家存亡之事。而有所因有次第。则草茅之士。亦有可言之义者。亦朱子之说。退溪先生。田徐辈人。岂肯尊尚师法。第其谨守朱门成法。似亦贤于今之君子矣。然而关系斯文之兴丧。国家之存亡。则又开可言之路。此两义者。正当量时度义而处之。不可执一说而攻一说。以朱子而骂朱子也。如此则是孟子所谓举一而废百者也。岂所谓道哉。延平两宋之时。则朝著之间。斥和之臣。磊落相望。扶植正义。当是时。不在其位者。无事于言也。谨守前一说。塞兑括囊。可也。年前之事。究竟为
先师乎。在星田。则勒搆不讥之人。加以暗讥之罪。如恐不及。在吾师与先贤。则侵诬骂辱无复馀地而恬然不以为意。反使此汉。终始和平。何也。岂强弱悬殊。炎凉不得不然耶。至如遂非之戒。是欲使我诬服于诸公也。向使只就此汉。加此罪目而止。则固不足校矣。然以朱先生讥直不疑偿金事推之。则亦无诬服之义。况今田徐不但搏噬此汉。并辱既骨之华翁。而上及于宋之三先生者。罔有纪极。则虽我弱彼强。不得声讨。何忍诬服而乞怜乎。来教自纲目胡氏说。至两宋所处之义。虽终日言之。不过献昭陵之说也。夫身不出则言不出。固朱子之说也。系国家存亡之事。而有所因有次第。则草茅之士。亦有可言之义者。亦朱子之说。退溪先生。田徐辈人。岂肯尊尚师法。第其谨守朱门成法。似亦贤于今之君子矣。然而关系斯文之兴丧。国家之存亡。则又开可言之路。此两义者。正当量时度义而处之。不可执一说而攻一说。以朱子而骂朱子也。如此则是孟子所谓举一而废百者也。岂所谓道哉。延平两宋之时。则朝著之间。斥和之臣。磊落相望。扶植正义。当是时。不在其位者。无事于言也。谨守前一说。塞兑括囊。可也。年前之事。究竟为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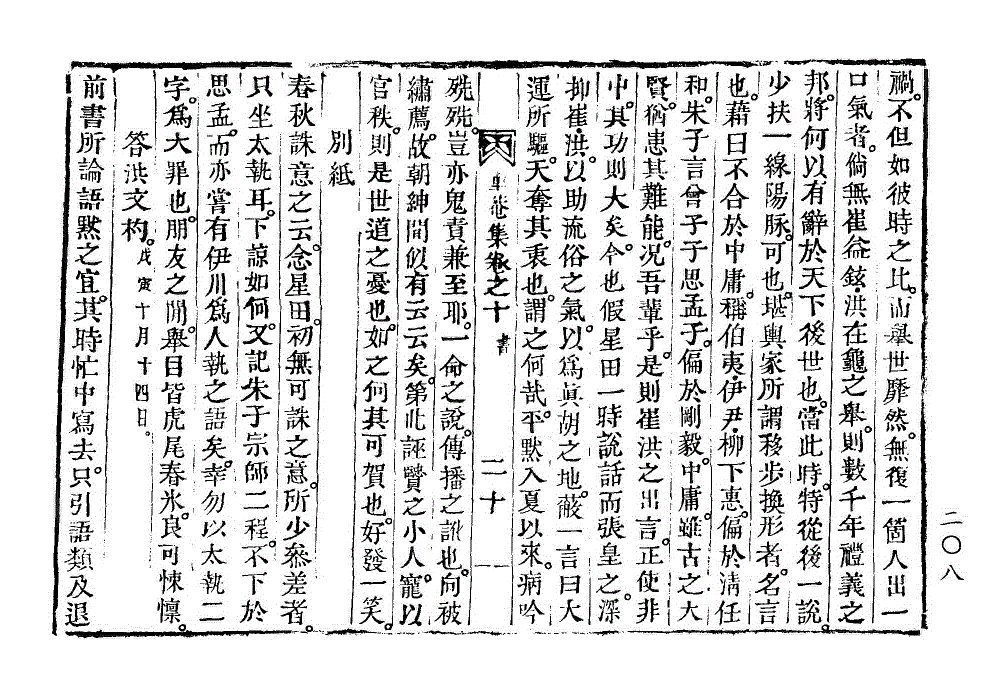 祸。不但如彼时之比。而举世靡然。无复一个人出一口气者。倘无崔益铉,洪在龟之举。则数千年礼义之邦。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当此时。特从后一说。少扶一线阳脉。可也。堪舆家所谓移步换形者。名言也。藉曰不合于中庸。称伯夷,伊尹,柳下惠。偏于清任和。朱子言曾子子思孟子。偏于刚毅。中庸。虽古之大贤。犹患其难能。况吾辈乎。是则崔洪之出言。正使非中。其功则大矣。今也假星田一时说话而张皇之。深抑崔,洪。以助流俗之气。以为真胡之地。蔽一言曰大运所驱。天夺其衷也。谓之何哉。平默入夏以来。病吟㱡㱡。岂亦鬼责兼至耶。一命之说。传播之讹也。向被绣荐。故朝绅间似有云云矣。第此诬贤之小人。宠以官秩。则是世道之忧也。如之何其可贺也。好发一笑。
祸。不但如彼时之比。而举世靡然。无复一个人出一口气者。倘无崔益铉,洪在龟之举。则数千年礼义之邦。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当此时。特从后一说。少扶一线阳脉。可也。堪舆家所谓移步换形者。名言也。藉曰不合于中庸。称伯夷,伊尹,柳下惠。偏于清任和。朱子言曾子子思孟子。偏于刚毅。中庸。虽古之大贤。犹患其难能。况吾辈乎。是则崔洪之出言。正使非中。其功则大矣。今也假星田一时说话而张皇之。深抑崔,洪。以助流俗之气。以为真胡之地。蔽一言曰大运所驱。天夺其衷也。谓之何哉。平默入夏以来。病吟㱡㱡。岂亦鬼责兼至耶。一命之说。传播之讹也。向被绣荐。故朝绅间似有云云矣。第此诬贤之小人。宠以官秩。则是世道之忧也。如之何其可贺也。好发一笑。别纸
春秋诛意之云。念星田。初无可诛之意。所少参差者。只坐太执耳。下谅如何。又记朱子宗师二程。不下于思孟。而亦尝有伊川为人执之语矣。幸勿以太执二字。为大罪也。朋友之閒。举目皆虎尾春冰。良可悚懔。
答洪文杓。(戊寅十月十四日。)
前书所论语默之宜。其时忙中写去。只引语类及退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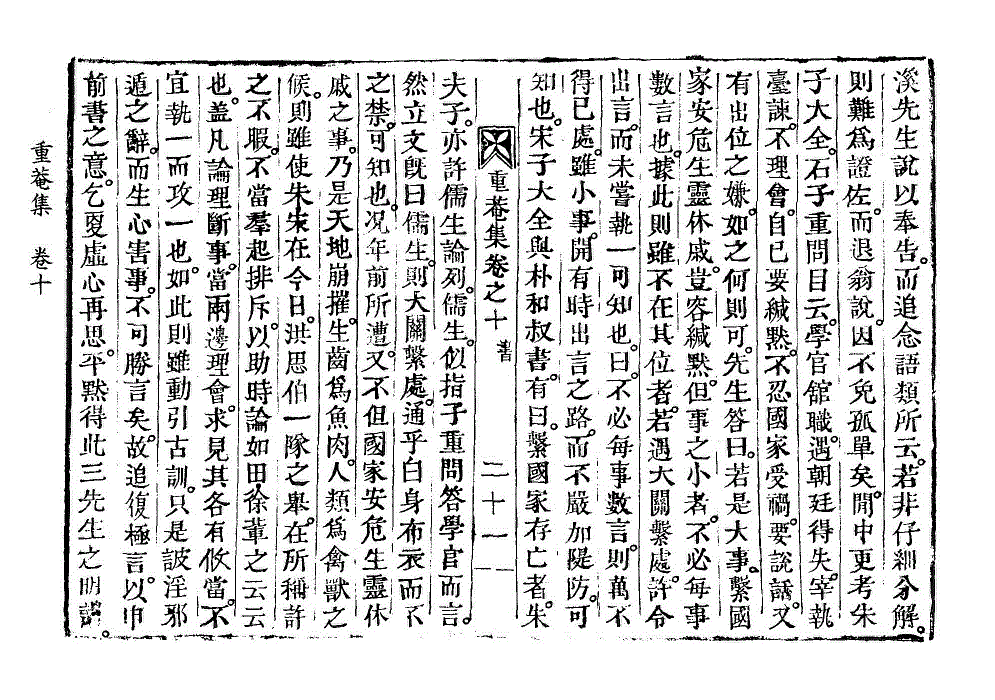 溪先生说以奉告。而追念语类所云。若非仔细分解。则难为證佐。而退翁说。因不免孤单矣。閒中更考朱子大全。石子重问目云。学官馆职。遇朝廷得失。宰执台谏。不理会。自已要缄默。不忍国家受祸。要说话。又有出位之嫌。如之何则可。先生答曰。若是大事。系国家安危生灵休戚。岂容缄默。但事之小者。不必每事数言也。据此则虽不在其位者。若遇大关系处。许令出言。而未尝执一可知也。曰。不必每事数言。则万不得已处。虽小事。开有时出言之路。而不严加堤防。可知也。宋子大全与朴和叔书。有曰。系国家存亡者。朱夫子。亦许儒生论列。儒生。似指子重问答学官而言。然立文既曰儒生。则大关系处。通乎白身布衣而不之禁。可知也。况年前所遭。又不但国家安危生灵休戚之事。乃是天地崩摧。生齿为鱼肉。人类为禽兽之候。则虽使朱,宋在今日。洪思伯一队之举。在所称许之不暇。不当群起排斥。以助时论如田,徐辈之云云也。盖凡论理断事。当两边理会。求见其各有攸当。不宜执一而攻一也。如此则虽动引古训。只是诐淫邪遁之辞。而生心害事。不可胜言矣。故追复极言。以申前书之意。乞更虚心再思。平默得此三先生之明谓。
溪先生说以奉告。而追念语类所云。若非仔细分解。则难为證佐。而退翁说。因不免孤单矣。閒中更考朱子大全。石子重问目云。学官馆职。遇朝廷得失。宰执台谏。不理会。自已要缄默。不忍国家受祸。要说话。又有出位之嫌。如之何则可。先生答曰。若是大事。系国家安危生灵休戚。岂容缄默。但事之小者。不必每事数言也。据此则虽不在其位者。若遇大关系处。许令出言。而未尝执一可知也。曰。不必每事数言。则万不得已处。虽小事。开有时出言之路。而不严加堤防。可知也。宋子大全与朴和叔书。有曰。系国家存亡者。朱夫子。亦许儒生论列。儒生。似指子重问答学官而言。然立文既曰儒生。则大关系处。通乎白身布衣而不之禁。可知也。况年前所遭。又不但国家安危生灵休戚之事。乃是天地崩摧。生齿为鱼肉。人类为禽兽之候。则虽使朱,宋在今日。洪思伯一队之举。在所称许之不暇。不当群起排斥。以助时论如田,徐辈之云云也。盖凡论理断事。当两边理会。求见其各有攸当。不宜执一而攻一也。如此则虽动引古训。只是诐淫邪遁之辞。而生心害事。不可胜言矣。故追复极言。以申前书之意。乞更虚心再思。平默得此三先生之明谓。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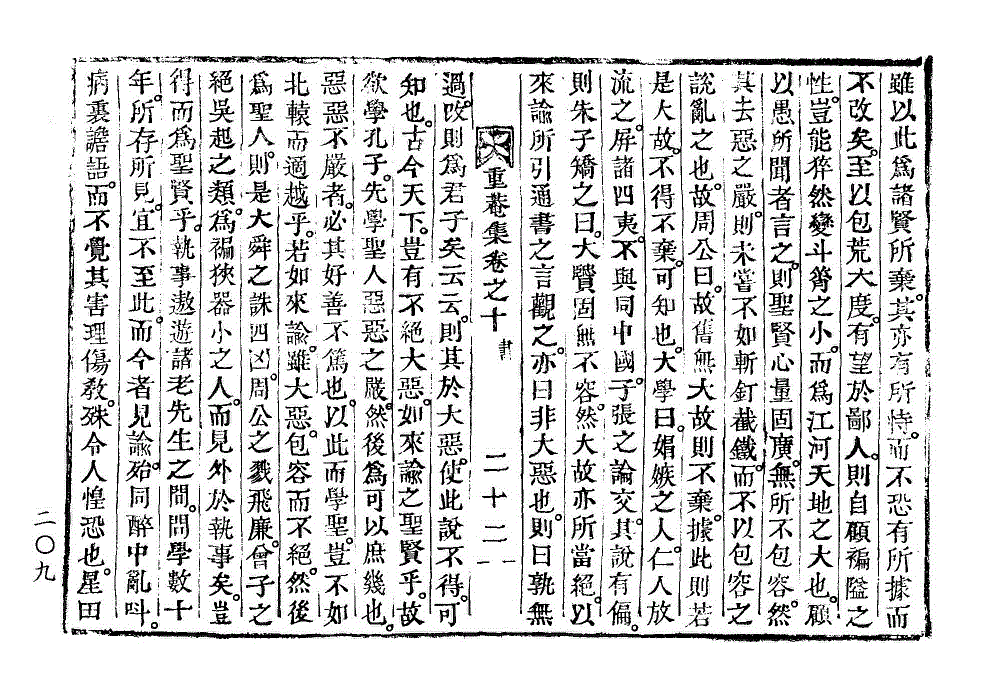 虽以此为诸贤所弃。其亦有所恃。而不恐有所据而不改矣。至以包荒大度。有望于鄙人。则自顾褊隘之性。岂能猝然变斗筲之小。而为江河天地之大也。顾以愚所闻者言之。则圣贤心量固广。无所不包容。然其去恶之严。则未尝不如斩钉截铁。而不以包容之说乱之也。故周公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据此则若是大故。不得不弃。可知也。大学曰。媢嫉之人。仁人放流之。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子张之论交。其说有偏。则朱子矫之曰。大贤固无不容。然大故亦所当绝。以来谕所引通书之言观之。亦曰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改则为君子矣云云。则其于大恶。使此说不得。可知也。古今天下。岂有不绝大恶。如来谕之圣贤乎。故欲学孔子。先学圣人恶恶之严。然后为可以庶几也。恶恶不严者。必其好善不笃也。以此而学圣。岂不如北辕而适越乎。若如来谕。虽大恶。包容而不绝。然后为圣人。则是大舜之诛四凶。周公之戮飞廉。曾子之绝吴起之类。为褊狭器小之人。而见外于执事矣。岂得而为圣贤乎。执事遨游诸老先生之间。问学数十年。所存所见。宜不至此。而今者见谕。殆同醉中乱叫。病里谵语。而不觉其害理伤教。殊令人惶恐也。星田
虽以此为诸贤所弃。其亦有所恃。而不恐有所据而不改矣。至以包荒大度。有望于鄙人。则自顾褊隘之性。岂能猝然变斗筲之小。而为江河天地之大也。顾以愚所闻者言之。则圣贤心量固广。无所不包容。然其去恶之严。则未尝不如斩钉截铁。而不以包容之说乱之也。故周公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据此则若是大故。不得不弃。可知也。大学曰。媢嫉之人。仁人放流之。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子张之论交。其说有偏。则朱子矫之曰。大贤固无不容。然大故亦所当绝。以来谕所引通书之言观之。亦曰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改则为君子矣云云。则其于大恶。使此说不得。可知也。古今天下。岂有不绝大恶。如来谕之圣贤乎。故欲学孔子。先学圣人恶恶之严。然后为可以庶几也。恶恶不严者。必其好善不笃也。以此而学圣。岂不如北辕而适越乎。若如来谕。虽大恶。包容而不绝。然后为圣人。则是大舜之诛四凶。周公之戮飞廉。曾子之绝吴起之类。为褊狭器小之人。而见外于执事矣。岂得而为圣贤乎。执事遨游诸老先生之间。问学数十年。所存所见。宜不至此。而今者见谕。殆同醉中乱叫。病里谵语。而不觉其害理伤教。殊令人惶恐也。星田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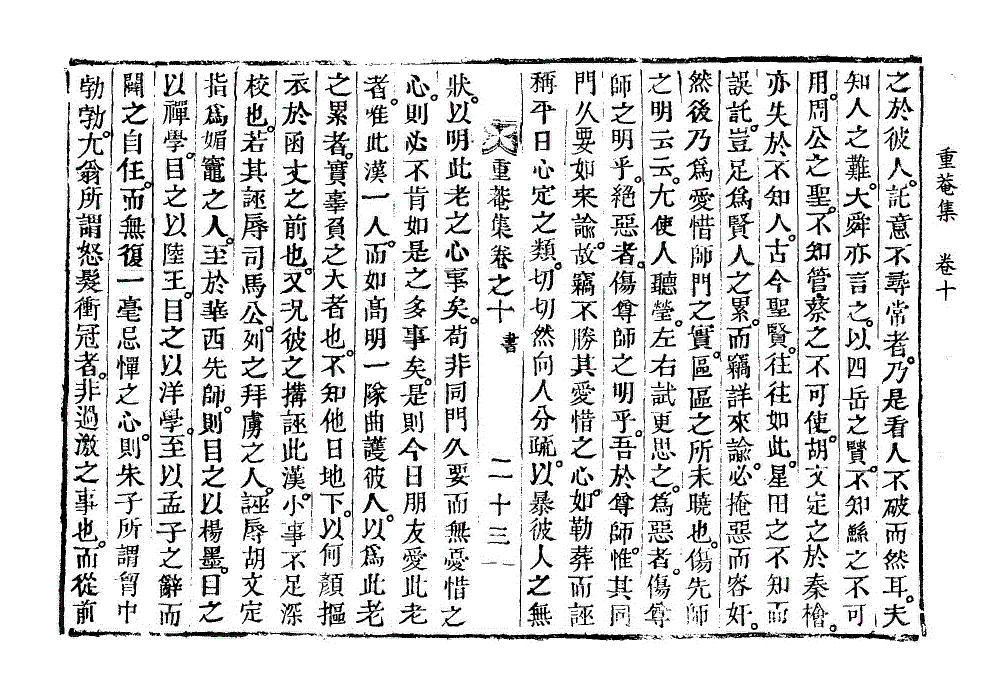 之于彼人。托意不寻常者。乃是看人不破而然耳。夫知人之难。大舜亦言之。以四岳之贤。不知鲧之不可用。周公之圣。不知管,蔡之不可使。胡文定之于秦桧。亦失于不知人。古今圣贤。往往如此。星田之不知而误托。岂足为贤人之累。而窃详来谕。必掩恶而容奸。然后乃为爱惜师门之实。区区之所未晓也。伤先师之明云云。尤使人听莹。左右试更思之。为恶者。伤尊师之明乎。绝恶者。伤尊师之明乎。吾于尊师。惟其同门久要如来谕。故窃不胜其爱惜之心。如勒葬而诬称平日心定之类。切切然向人分疏。以暴彼人之无状。以明此老之心事矣。苟非同门久要而无忧惜之心。则必不肯如是之多事矣。是则今日朋友爱此老者。唯此汉一人。而如高明一队曲护彼人。以为此老之累者。实辜负之大者也。不知他日地下。以何颜抠衣于函丈之前也。又况彼之搆诬此汉。小事不足深校也。若其诬辱司马公。列之拜虏之人。诬辱胡文定指为媚灶之人。至于华西先师。则目之以杨墨。目之以禅学。目之以陆王。目之以洋学。至以孟子之辞而辟之自任。而无复一毫忌惮之心。则朱子所谓胸中勃勃。尤翁所谓怒发冲冠者。非过激之事也。而从前
之于彼人。托意不寻常者。乃是看人不破而然耳。夫知人之难。大舜亦言之。以四岳之贤。不知鲧之不可用。周公之圣。不知管,蔡之不可使。胡文定之于秦桧。亦失于不知人。古今圣贤。往往如此。星田之不知而误托。岂足为贤人之累。而窃详来谕。必掩恶而容奸。然后乃为爱惜师门之实。区区之所未晓也。伤先师之明云云。尤使人听莹。左右试更思之。为恶者。伤尊师之明乎。绝恶者。伤尊师之明乎。吾于尊师。惟其同门久要如来谕。故窃不胜其爱惜之心。如勒葬而诬称平日心定之类。切切然向人分疏。以暴彼人之无状。以明此老之心事矣。苟非同门久要而无忧惜之心。则必不肯如是之多事矣。是则今日朋友爱此老者。唯此汉一人。而如高明一队曲护彼人。以为此老之累者。实辜负之大者也。不知他日地下。以何颜抠衣于函丈之前也。又况彼之搆诬此汉。小事不足深校也。若其诬辱司马公。列之拜虏之人。诬辱胡文定指为媚灶之人。至于华西先师。则目之以杨墨。目之以禅学。目之以陆王。目之以洋学。至以孟子之辞而辟之自任。而无复一毫忌惮之心。则朱子所谓胸中勃勃。尤翁所谓怒发冲冠者。非过激之事也。而从前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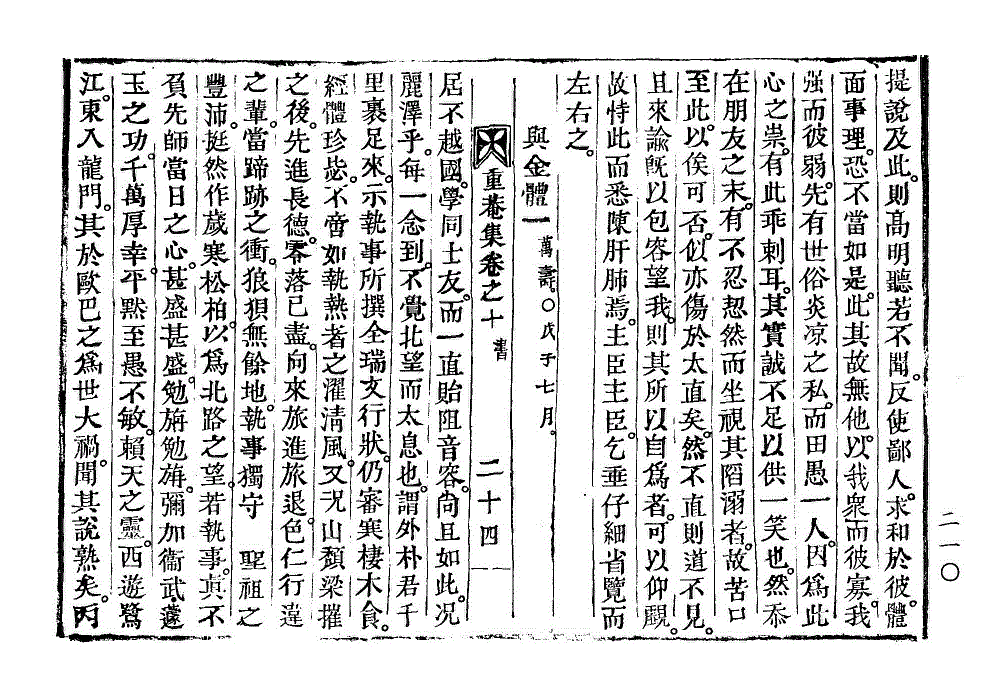 提说及此。则高明听若不闻。反使鄙人。求和于彼。体面事理。恐不当如是。此其故无他。以我众而彼寡。我强而彼弱。先有世俗炎凉之私。而田愚一人。因为此心之祟。有此乖剌耳。其实诚不足以供一笑也。然忝在朋友之末。有不忍恝然而坐视其陷溺者。故苦口至此。以俟可否。似亦伤于太直矣。然不直则道不见。且来谕既以包容望我。则其所以自为者。可以仰觑。故恃此而悉陈肝肺焉。主臣主臣。乞垂仔细省览而左右之。
提说及此。则高明听若不闻。反使鄙人。求和于彼。体面事理。恐不当如是。此其故无他。以我众而彼寡。我强而彼弱。先有世俗炎凉之私。而田愚一人。因为此心之祟。有此乖剌耳。其实诚不足以供一笑也。然忝在朋友之末。有不忍恝然而坐视其陷溺者。故苦口至此。以俟可否。似亦伤于太直矣。然不直则道不见。且来谕既以包容望我。则其所以自为者。可以仰觑。故恃此而悉陈肝肺焉。主臣主臣。乞垂仔细省览而左右之。与金体一(万寿。○戊子七月。)
居不越国。学同士友。而一直贻阻音容。尚且如此。况丽泽乎。每一念到。不觉北望而太息也。谓外朴君千里裹足来。示执事所撰全瑞文行状。仍审寒栖木食。经体珍毖。不啻如执热者之濯清风。又况山颓梁摧之后。先进长德。零落已尽。向来旅进旅退。色仁行违之辈。当蹄迹之冲。狼狈无馀地。执事独守 圣祖之丰沛。挺然作岁寒松柏。以为北路之望。若执事。真不负先师当日之心。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弥加卫武,蘧玉之功。千万厚幸。平默至愚不敏。赖天之灵。西游鹭江。东入龙门。其于欧巴之为世大祸。闻其说熟矣。丙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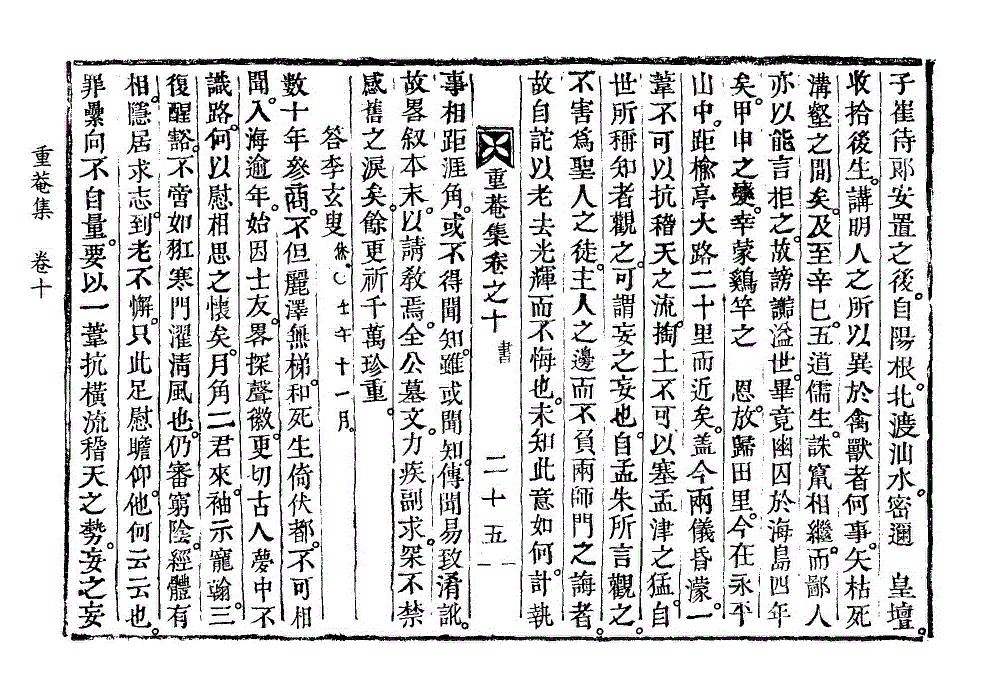 子崔侍郎安置之后。自阳根。北渡汕水。密迩 皇坛。收拾后生。讲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事。矢枯死沟壑之间矣。及至辛巳。五道儒生。诛窜相继。而鄙人亦以能言拒之。故谤讟溢世。毕竟幽囚于海岛四年矣。甲申之变。幸蒙鸡竿之 恩。放归田里。今在永平山中。距榆亭大路二十里而近矣。盖今两仪昏濛。一苇不可以抗稽天之流。掏土不可以塞孟津之猛。自世所称知者观之。可谓妄之妄也。自孟朱所言观之。不害为圣人之徒。主人之边而不负两师门之诲者。故自詑以老去光辉而不悔也。未知此意如何。计执事相距涯角。或不得闻知。虽或闻知。传闻易致淆讹。故略叙本末。以请教焉。全公墓文。力疾副求。深不禁感旧之泪矣。馀更祈千万珍重。
子崔侍郎安置之后。自阳根。北渡汕水。密迩 皇坛。收拾后生。讲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事。矢枯死沟壑之间矣。及至辛巳。五道儒生。诛窜相继。而鄙人亦以能言拒之。故谤讟溢世。毕竟幽囚于海岛四年矣。甲申之变。幸蒙鸡竿之 恩。放归田里。今在永平山中。距榆亭大路二十里而近矣。盖今两仪昏濛。一苇不可以抗稽天之流。掏土不可以塞孟津之猛。自世所称知者观之。可谓妄之妄也。自孟朱所言观之。不害为圣人之徒。主人之边而不负两师门之诲者。故自詑以老去光辉而不悔也。未知此意如何。计执事相距涯角。或不得闻知。虽或闻知。传闻易致淆讹。故略叙本末。以请教焉。全公墓文。力疾副求。深不禁感旧之泪矣。馀更祈千万珍重。答李玄叟(炰。○壬午十一月。)
数十年参商。不但丽泽无梯。和死生倚伏都。不可相闻。入海逾年。始因士友。略探声徽。更切古人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之怀矣。月角二君来。袖示宠翰。三复醒豁。不啻如羾寒门濯清风也。仍审穷阴。经体有相。隐居求志。到老不懈。只此足慰瞻仰。他何云云也。罪累向不自量。要以一苇抗横流稽天之势。妄之妄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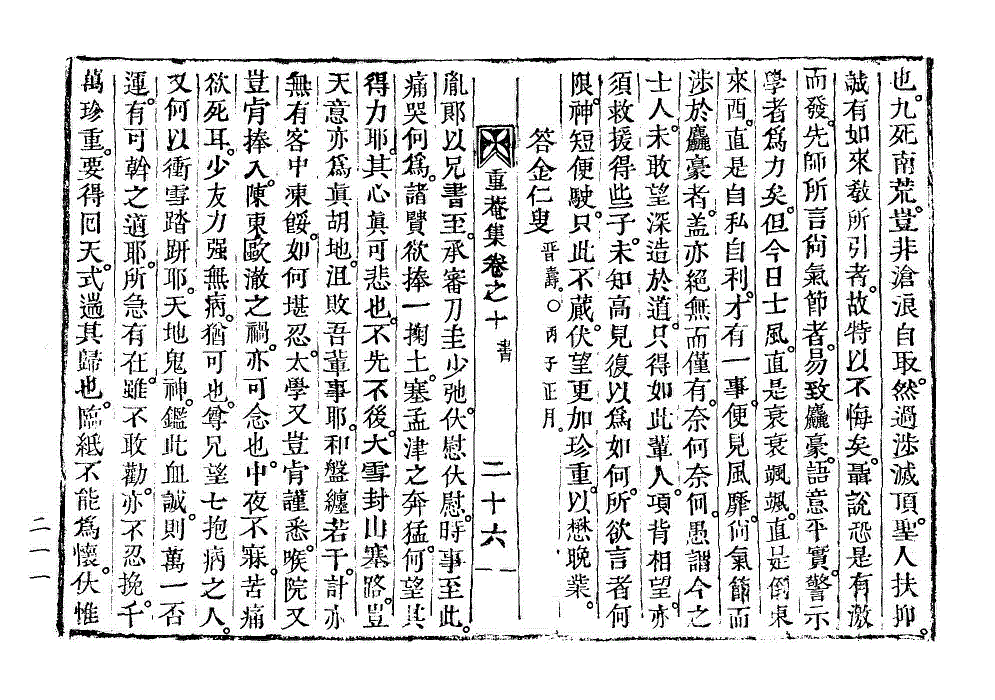 也。九死南荒。岂非沧浪自取。然过涉灭顶。圣人扶抑。诚有如来教所引者。故特以不悔矣。聂说恐是有激而发。先师所言尚气节者。易致粗豪。语意平实。警示学者为力矣。但今日士风。直是衰衰飒飒。直是倒东来西。直是自私自利。才有一事。便见风靡。尚气节而涉于粗豪者。盖亦绝无而仅有。奈何奈何。愚谓今之士人。未敢望深造于道。只得如此辈人。项背相望。亦须救援得些子。未知高见复以为如何。所欲言者何限。神短便驶。只此不蒇。伏望更加珍重。以懋晚业。
也。九死南荒。岂非沧浪自取。然过涉灭顶。圣人扶抑。诚有如来教所引者。故特以不悔矣。聂说恐是有激而发。先师所言尚气节者。易致粗豪。语意平实。警示学者为力矣。但今日士风。直是衰衰飒飒。直是倒东来西。直是自私自利。才有一事。便见风靡。尚气节而涉于粗豪者。盖亦绝无而仅有。奈何奈何。愚谓今之士人。未敢望深造于道。只得如此辈人。项背相望。亦须救援得些子。未知高见复以为如何。所欲言者何限。神短便驶。只此不蒇。伏望更加珍重。以懋晚业。答金仁叟(晋寿。○丙子正月。)
胤郎以兄书至。承审刀圭少弛。伏慰伏慰。时事至此。痛哭何为。诸贤欲捧一掬土。塞孟津之奔猛。何望其得力耶。其心真可悲也。不先不后。大雪封山塞路。岂天意亦为真胡地。沮败吾辈事耶。和盘缠若干。计亦无有客中冻馁。如何堪忍。太学又岂肯谨悉。喉院又岂肯捧入。陈东欧澈之祸。亦可念也。中夜不寐。苦痛欲死耳。少友力强无病。犹可也。尊兄望七抱病之人。又何以冲雪踏趼耶。天地鬼神。鉴此血诚。则万一否运。有可斡之道耶。所急有在。虽不敢劝。亦不忍挽。千万珍重。要得回天。式遄其归也。临纸不能为怀。伏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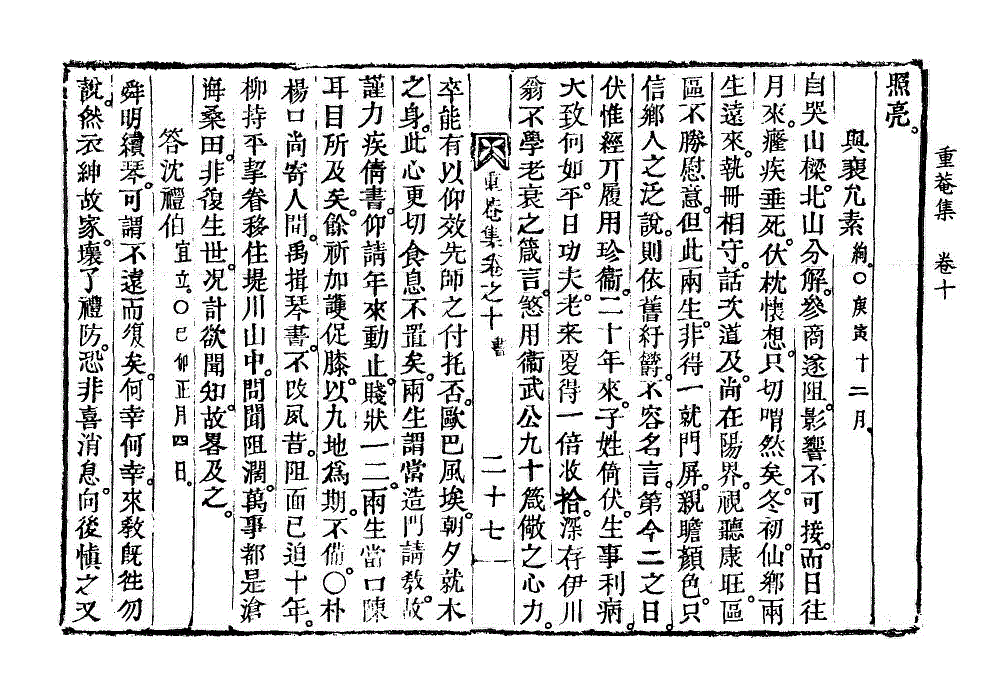 照亮。
照亮。与裴允素(绚。○庚寅十二月。)
自哭山梁。北山分解。参商遂阻。影响不可接。而日往月来。癃疾垂死。伏枕怀想。只切喟然矣。冬初。仙乡两生远来。执册相守。话次道及。尚在阳界。视听康旺。区区不胜慰意。但此两生。非得一就门屏。亲瞻颜色。只信乡人之泛说。则依旧纡郁。不容名言。第今二之日。伏惟经丌履用珍卫。二十年来。子姓倚伏。生事利病。大致何如。平日功夫。老来更得一倍收拾。深存伊川翁不学老衰之箴言。煞用卫武公九十箴儆之心力。卒能有以仰效先师之付托否。欧巴风埃。朝夕就木之身。此心更切食息不置矣。两生谓当造门请教。故谨力疾倩书。仰请年来动止。贱状一二。两生当口陈耳目所及矣。馀祈加护促膝。以九地为期。不备。○朴杨口尚寄人间。禹揖琴书。不改夙昔。阻面已迫十年。柳持平挈眷移住堤川山中。问闻阻阔。万事都是沧海桑田。非复生世。况计欲闻知故略及之。
答沈礼伯(宜立。○己卯正月四日。)
舜明续琴。可谓不远而复矣。何幸何幸。来教既往勿说。然衣绅故家。坏了礼防。恐非喜消息。向后慎之又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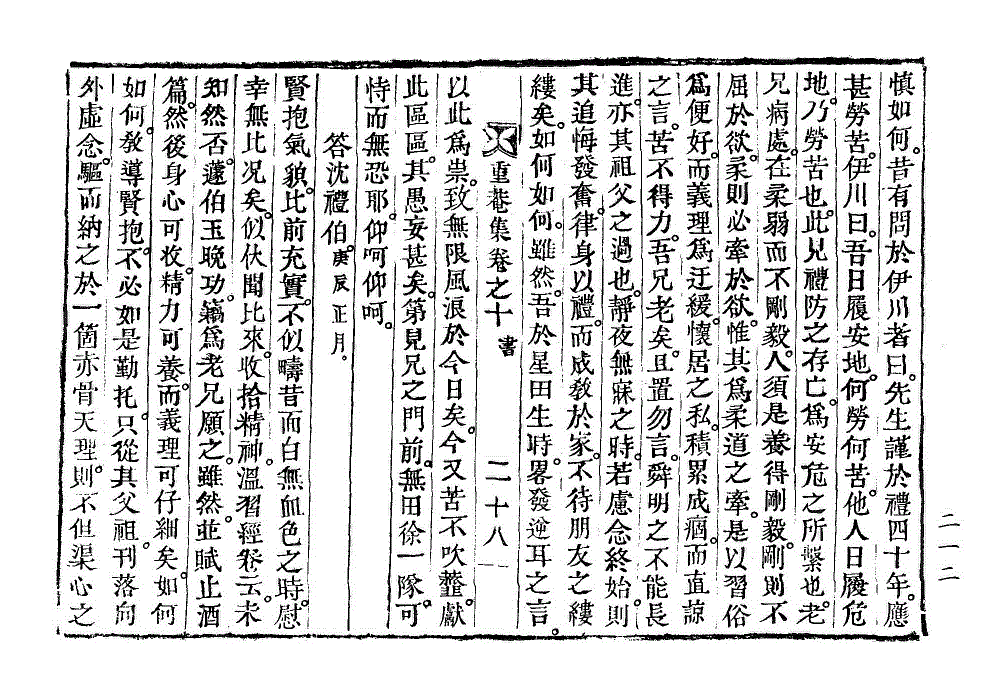 慎如何。昔有问于伊川者曰。先生谨于礼四十年。应甚劳苦。伊川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他人日履危地。乃劳苦也。此见礼防之存亡。为安危之所系也。老兄病处。在柔弱而不刚毅。人须是养得刚毅。刚则不屈于欲。柔则必牵于欲。惟其为柔道之牵。是以习俗为便好。而义理为迂缓。怀居之私。积累成痼。而直谅之言。苦不得力。吾兄老矣。且置勿言。舜明之不能长进。亦其祖父之过也。静夜无寐之时。若虑念终始。则其追悔发奋。律身以礼。而成教于家。不待朋友之缕缕矣。如何如何。虽然。吾于星田生时。略发逆耳之言。以此为祟。致无限风浪于今日矣。今又苦不吹齑。献此区区。其愚妄甚矣。第见兄之门前。无田徐一队。可恃而无恐耶。仰呵仰呵。
慎如何。昔有问于伊川者曰。先生谨于礼四十年。应甚劳苦。伊川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他人日履危地。乃劳苦也。此见礼防之存亡。为安危之所系也。老兄病处。在柔弱而不刚毅。人须是养得刚毅。刚则不屈于欲。柔则必牵于欲。惟其为柔道之牵。是以习俗为便好。而义理为迂缓。怀居之私。积累成痼。而直谅之言。苦不得力。吾兄老矣。且置勿言。舜明之不能长进。亦其祖父之过也。静夜无寐之时。若虑念终始。则其追悔发奋。律身以礼。而成教于家。不待朋友之缕缕矣。如何如何。虽然。吾于星田生时。略发逆耳之言。以此为祟。致无限风浪于今日矣。今又苦不吹齑。献此区区。其愚妄甚矣。第见兄之门前。无田徐一队。可恃而无恐耶。仰呵仰呵。答沈礼伯。(庚辰正月。)
贤抱气貌。比前充实。不似畴昔面白无血色之时。慰幸无此况矣。似伏闻比来。收拾精神。温习经卷云。未知然否。蘧伯玉晚功。窃为老兄愿之。虽然。并赋止酒篇。然后身心可收。精力可养。而义理可仔细矣。如何如何。教导贤抱。不必如是勤托。只从其父祖。刊落向外虚念。驱而纳之于一个赤骨天理。则不但渠心之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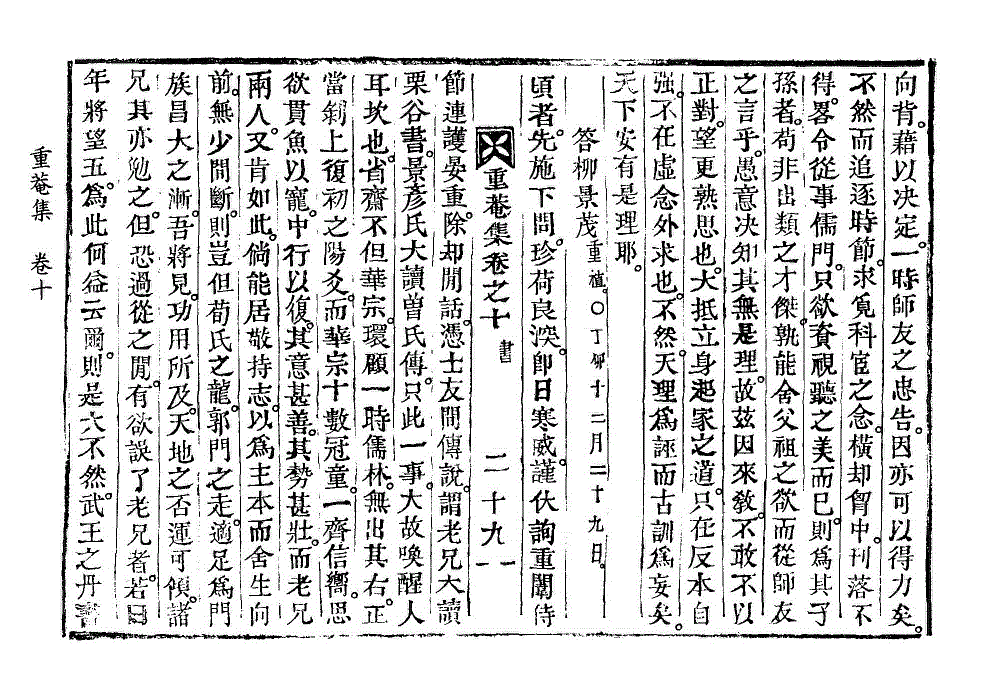 向背。藉以决定。一时师友之忠告。因亦可以得力矣。不然而追逐时节。求觅科宦之念。横却胸中。刊落不得。略令从事儒门。只欲资视听之美而已。则为其子孙者。苟非出类之才杰。执能舍父祖之欲而从师友之言乎。愚意决知其无是理。故玆因来教。不敢不以正对。望更熟思也。大抵立身起家之道。只在反本自强。不在虚念外求也。不然。天理为诬而古训为妄矣。天下安有是理耶。
向背。藉以决定。一时师友之忠告。因亦可以得力矣。不然而追逐时节。求觅科宦之念。横却胸中。刊落不得。略令从事儒门。只欲资视听之美而已。则为其子孙者。苟非出类之才杰。执能舍父祖之欲而从师友之言乎。愚意决知其无是理。故玆因来教。不敢不以正对。望更熟思也。大抵立身起家之道。只在反本自强。不在虚念外求也。不然。天理为诬而古训为妄矣。天下安有是理耶。答柳景茂(重植。○丁卯十二月二十九日。)
顷者。先施下问。珍荷良深。即日寒威。谨伏询重闱侍节连护晏重。除却閒话。凭士友间传说。谓老兄大读栗谷书。景彦氏大读曾氏传。只此一事。大故唤醒人耳坎也。省斋不但华宗。环顾一时儒林。无出其右。正当剥上复初之阳爻。而华宗十数冠童。一齐信向。思欲贯鱼以宠。中行以复。其意甚善。其势甚壮。而老兄两人。又肯如此。倘能居敬持志。以为主本而舍生向前。无少间断。则岂但荀氏之龙。郭门之走。适足为门族昌大之渐。吾将见。功用所及。天地之否运可倾。诸兄其亦勉之。但恐过从之閒。有欲误了老兄者。若曰年将望五。为此何益云尔。则是大不然。武王之丹书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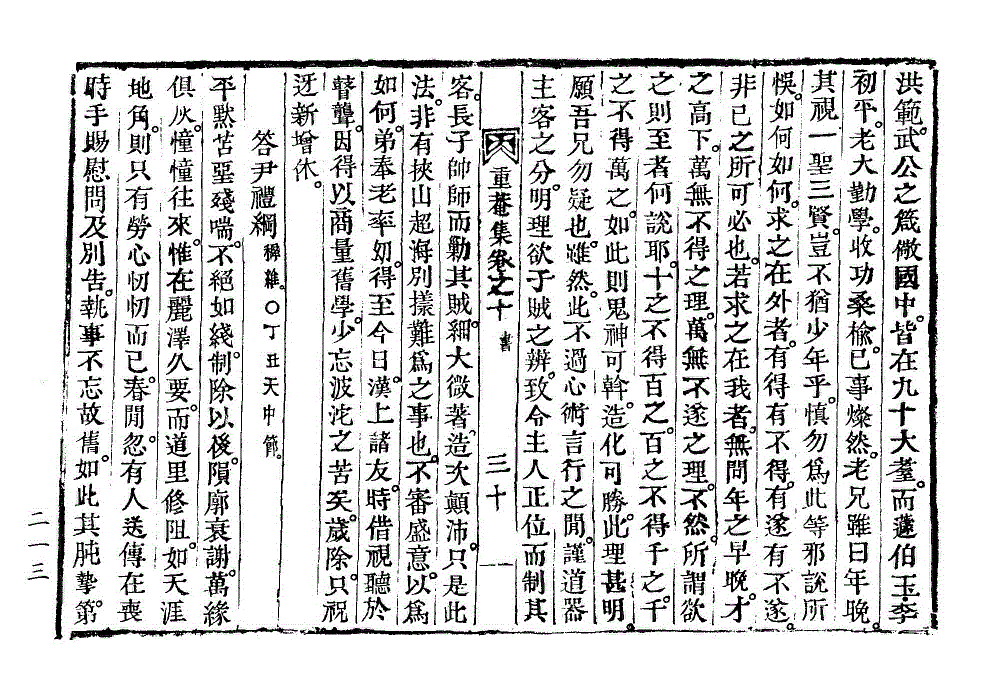 洪范。武公之箴儆国中。皆在九十大耋。而蘧伯玉,李初平。老大勤学。收功桑榆。已事灿然。老兄虽曰年晚。其视一圣三贤。岂不犹少年乎。慎勿为此等邪说所误。如何如何。求之在外者。有得有不得。有遂有不遂。非已之所可必也。若求之在我者。无问年之早晚。才之高下。万无不得之理。万无不遂之理。不然。所谓欲之则至者何说耶。十之不得百之。百之不得千之。千之不得万之。如此则鬼神可斡。造化可胜。此理甚明。愿吾兄勿疑也。虽然。此不过心术言行之閒。谨道器主客之分。明理欲子贼之辨。致令主人正位而制其客。长子帅师而剿其贼。细大微著。造次颠沛。只是此法。非有挟山超海别㨾难为之事也。不审盛意。以为如何。弟奉老率幼。得至今日。汉上诸友。时借视听于瞽聋。因得以商量旧学。少忘波沱之苦矣。岁除。只祝迓新增休。
洪范。武公之箴儆国中。皆在九十大耋。而蘧伯玉,李初平。老大勤学。收功桑榆。已事灿然。老兄虽曰年晚。其视一圣三贤。岂不犹少年乎。慎勿为此等邪说所误。如何如何。求之在外者。有得有不得。有遂有不遂。非已之所可必也。若求之在我者。无问年之早晚。才之高下。万无不得之理。万无不遂之理。不然。所谓欲之则至者何说耶。十之不得百之。百之不得千之。千之不得万之。如此则鬼神可斡。造化可胜。此理甚明。愿吾兄勿疑也。虽然。此不过心术言行之閒。谨道器主客之分。明理欲子贼之辨。致令主人正位而制其客。长子帅师而剿其贼。细大微著。造次颠沛。只是此法。非有挟山超海别㨾难为之事也。不审盛意。以为如何。弟奉老率幼。得至今日。汉上诸友。时借视听于瞽聋。因得以商量旧学。少忘波沱之苦矣。岁除。只祝迓新增休。答尹礼纲(稚维。○丁丑天中节。)
平默苫垩残喘。不绝如线。制除以后。陨廓衰谢。万缘俱灰。憧憧往来。惟在丽泽久要。而道里修阻。如天涯地角。则只有劳心忍忍而已。春閒。忽有人送传在丧时手赐慰问及别告。执事不忘故旧。如此其肫挚。第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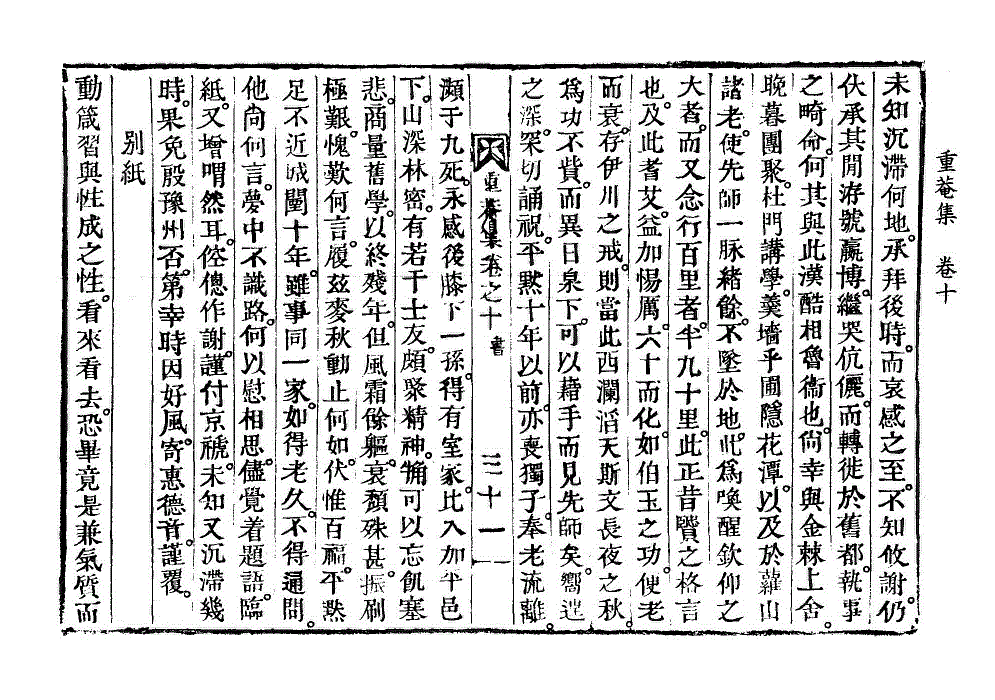 未知沉滞何地。承拜后时。而哀感之至。不知攸谢。仍伏承其閒荐号嬴博。继哭伉俪。而转徙于旧都。执事之畸命。何其与此汉酷相鲁卫也。尚幸与金棘上舍。晚暮团聚。杜门讲学。羹墙乎圃隐花潭。以及于萝山诸老。使先师一脉绪馀。不坠于地。此为唤醒钦仰之大者。而又念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正昔贤之格言也。及此耆艾。益加惕厉。六十而化。如伯玉之功。便老而衰。存伊川之戒。则当此西澜滔天斯文长夜之秋。为功不赀。而异日泉下。可以藉手而见先师矣。向𨓏之深。深切诵祝。平默十年以前。亦丧独子。奉老流离。濒于九死。永感后膝下一孙。得有室家。比入加平邑下。山深林密。有若干士友。颇聚精神。觕可以忘饥塞悲。商量旧学。以终残年。但风霜馀躯。衰颓殊甚。振刷极艰。愧叹何言。履玆麦秋动止何如。伏惟百福。平默足不近城闉十年。虽事同一家。如得老久。不得通问。他尚何言。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尽觉着题语。临纸。又增喟然耳。倥偬作谢。谨付京禠。未知又沉滞几时。果免殷豫州否。第幸时因好风。寄惠德音。谨覆。
未知沉滞何地。承拜后时。而哀感之至。不知攸谢。仍伏承其閒荐号嬴博。继哭伉俪。而转徙于旧都。执事之畸命。何其与此汉酷相鲁卫也。尚幸与金棘上舍。晚暮团聚。杜门讲学。羹墙乎圃隐花潭。以及于萝山诸老。使先师一脉绪馀。不坠于地。此为唤醒钦仰之大者。而又念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正昔贤之格言也。及此耆艾。益加惕厉。六十而化。如伯玉之功。便老而衰。存伊川之戒。则当此西澜滔天斯文长夜之秋。为功不赀。而异日泉下。可以藉手而见先师矣。向𨓏之深。深切诵祝。平默十年以前。亦丧独子。奉老流离。濒于九死。永感后膝下一孙。得有室家。比入加平邑下。山深林密。有若干士友。颇聚精神。觕可以忘饥塞悲。商量旧学。以终残年。但风霜馀躯。衰颓殊甚。振刷极艰。愧叹何言。履玆麦秋动止何如。伏惟百福。平默足不近城闉十年。虽事同一家。如得老久。不得通问。他尚何言。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尽觉着题语。临纸。又增喟然耳。倥偬作谢。谨付京禠。未知又沉滞几时。果免殷豫州否。第幸时因好风。寄惠德音。谨覆。别纸
动箴习与性成之性。看来看去。恐毕竟是兼气质而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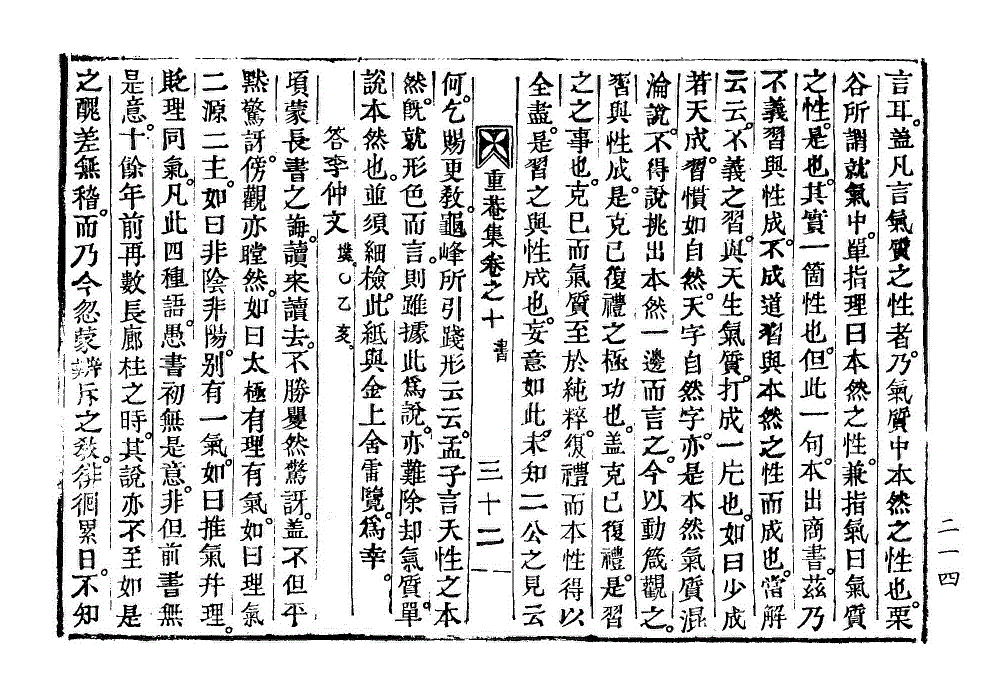 言耳。盖凡言气质之性者。乃气质中本然之性也。栗谷所谓就气中。单指理曰本然之性。兼指气曰气质之性。是也。其实一个性也。但此一句。本出商书。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不成道习与本然之性而成也。当解云云。不义之习。与天生气质。打成一片也。如曰少成若天成。习惯如自然。天字自然字。亦是本然气质混沦说。不得说挑出本然一边而言之。今以动箴观之。习与性成。是克己复礼之极功也。盖克己复礼。是习之之事也。克己而气质至于纯粹。复礼而本性得以全尽。是习之与性成也。妄意如此。未知二公之见云何。乞赐更教。龟峰所引践形云云。孟子言天性之本然。既就形色而言。则虽据此为说。亦难除却气质。单说本然也。并须细检。此纸与金上舍雷览。为幸。
言耳。盖凡言气质之性者。乃气质中本然之性也。栗谷所谓就气中。单指理曰本然之性。兼指气曰气质之性。是也。其实一个性也。但此一句。本出商书。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不成道习与本然之性而成也。当解云云。不义之习。与天生气质。打成一片也。如曰少成若天成。习惯如自然。天字自然字。亦是本然气质混沦说。不得说挑出本然一边而言之。今以动箴观之。习与性成。是克己复礼之极功也。盖克己复礼。是习之之事也。克己而气质至于纯粹。复礼而本性得以全尽。是习之与性成也。妄意如此。未知二公之见云何。乞赐更教。龟峰所引践形云云。孟子言天性之本然。既就形色而言。则虽据此为说。亦难除却气质。单说本然也。并须细检。此纸与金上舍雷览。为幸。答李仲文(墣。○乙亥。)
顷蒙长书之诲。读来读去。不胜矍然惊讶。盖不但平默惊讶。傍观亦瞠然。如曰太极有理有气。如曰理气二源二主。如曰非阴非阳。别有一气。如曰推气并理。贬理同气。凡此四种语。愚书初无是意。非但前书无是意。十馀年前再数长廊柱之时。其说亦不至如是之丑差无稽。而乃今忽蒙辨斥之教。徘徊累日。不知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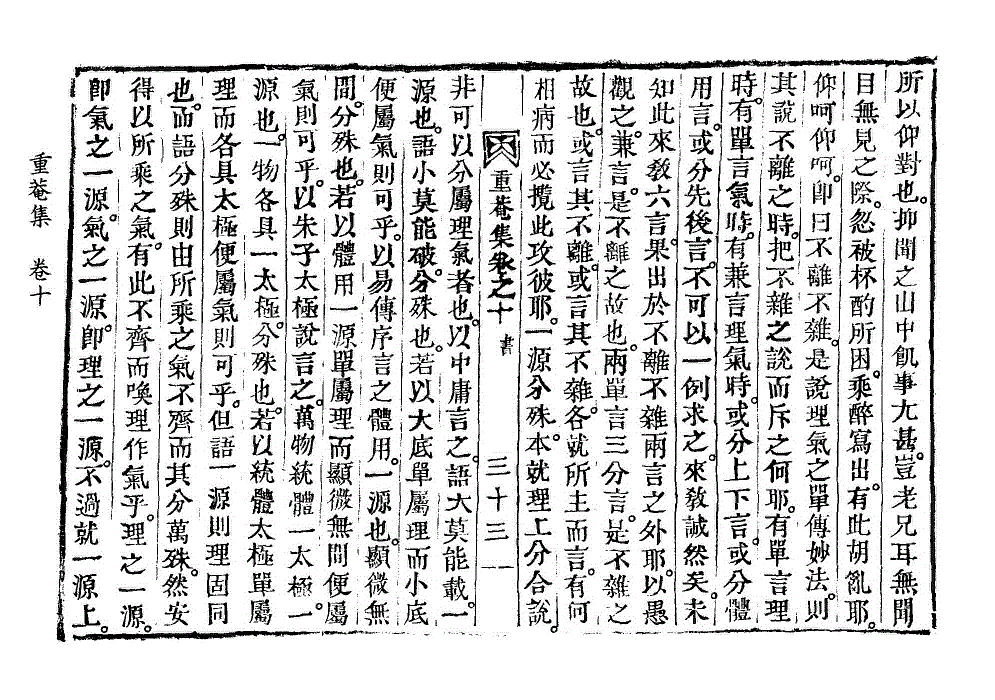 所以仰对也。抑闻之山中饥事尤甚。岂老兄耳无闻目无见之际。忽被杯酌所困。乘醉写出。有此胡乱耶。仰呵仰呵。即曰不离不杂。是说理气之单传妙法。则其说不离之时。把不杂之说而斥之何耶。有单言理时。有单言气时。有兼言理气时。或分上下言。或分体用言。或分先后言。不可以一例求之。来教诚然矣。未知此来教六言。果出于不离不杂两言之外耶。以愚观之。兼言。是不离之故也。两单言三分言。是不杂之故也。或言其不离。或言其不杂。各就所主而言。有何相病而必揽此攻彼耶。一源分殊。本就理上分合说。非可以分属理气者也。以中庸言之。语大莫能载。一源也。语小莫能破。分殊也。若以大底单属理而小底便属气则可乎。以易传序言之体用。一源也。显微无间。分殊也。若以体用一源单属理而显微无间便属气则可乎。以朱子太极说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一源也。一物各具一太极。分殊也。若以统体太极单属理而各具太极便属气则可乎。但语一源则理固同也。而语分殊则由所乘之气不齐而其分万殊。然安得以所乘之气。有此不齐而唤理作气乎。理之一源。即气之一源。气之一源。即理之一源。不过就一源上。
所以仰对也。抑闻之山中饥事尤甚。岂老兄耳无闻目无见之际。忽被杯酌所困。乘醉写出。有此胡乱耶。仰呵仰呵。即曰不离不杂。是说理气之单传妙法。则其说不离之时。把不杂之说而斥之何耶。有单言理时。有单言气时。有兼言理气时。或分上下言。或分体用言。或分先后言。不可以一例求之。来教诚然矣。未知此来教六言。果出于不离不杂两言之外耶。以愚观之。兼言。是不离之故也。两单言三分言。是不杂之故也。或言其不离。或言其不杂。各就所主而言。有何相病而必揽此攻彼耶。一源分殊。本就理上分合说。非可以分属理气者也。以中庸言之。语大莫能载。一源也。语小莫能破。分殊也。若以大底单属理而小底便属气则可乎。以易传序言之体用。一源也。显微无间。分殊也。若以体用一源单属理而显微无间便属气则可乎。以朱子太极说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一源也。一物各具一太极。分殊也。若以统体太极单属理而各具太极便属气则可乎。但语一源则理固同也。而语分殊则由所乘之气不齐而其分万殊。然安得以所乘之气。有此不齐而唤理作气乎。理之一源。即气之一源。气之一源。即理之一源。不过就一源上。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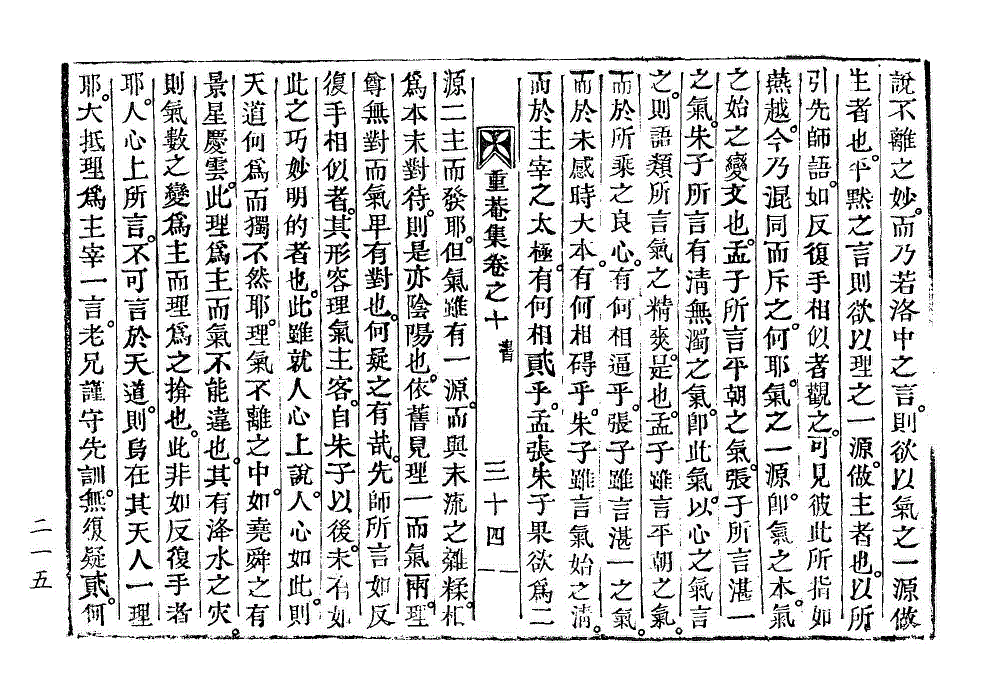 说不离之妙。而乃若洛中之言。则欲以气之一源做生者也。平默之言则欲以理之一源。做主者也。以所引先师语。如反复手相似者观之。可见彼此所指如燕越。今乃混同而斥之。何耶。气之一源。即气之本。气之始之变文也。孟子所言平朝之气。张子所言湛一之气。朱子所言有清无浊之气。即此气。以心之气言之。则语类所言气之精爽。是也。孟子虽言平朝之气。而于所乘之良心。有何相逼乎。张子虽言湛一之气。而于未感时大本。有何相碍乎。朱子虽言气始之清。而于主宰之太极。有何相贰乎。孟,张,朱子果欲为二源二主而发耶。但气虽有一源。而与末流之杂糅。相为本末对待。则是亦阴阳也。依旧见理一而气两。理尊无对而气卑有对也。何疑之有哉。先师所言如反复手相似者。其形容理气主客。自朱子以后。未有如此之巧妙明的者也。此虽就人心上说。人心如此。则天道何为而独不然耶。理气不离之中。如尧舜之有景星庆云。此理为主而气不能违也。其有洚水之灾。则气数之变为主而理为之掩也。此非如反复手者耶。人心上所言。不可言于天道。则乌在其天人一理耶。大抵理为主宰一言。老兄谨守先训。无复疑贰。何
说不离之妙。而乃若洛中之言。则欲以气之一源做生者也。平默之言则欲以理之一源。做主者也。以所引先师语。如反复手相似者观之。可见彼此所指如燕越。今乃混同而斥之。何耶。气之一源。即气之本。气之始之变文也。孟子所言平朝之气。张子所言湛一之气。朱子所言有清无浊之气。即此气。以心之气言之。则语类所言气之精爽。是也。孟子虽言平朝之气。而于所乘之良心。有何相逼乎。张子虽言湛一之气。而于未感时大本。有何相碍乎。朱子虽言气始之清。而于主宰之太极。有何相贰乎。孟,张,朱子果欲为二源二主而发耶。但气虽有一源。而与末流之杂糅。相为本末对待。则是亦阴阳也。依旧见理一而气两。理尊无对而气卑有对也。何疑之有哉。先师所言如反复手相似者。其形容理气主客。自朱子以后。未有如此之巧妙明的者也。此虽就人心上说。人心如此。则天道何为而独不然耶。理气不离之中。如尧舜之有景星庆云。此理为主而气不能违也。其有洚水之灾。则气数之变为主而理为之掩也。此非如反复手者耶。人心上所言。不可言于天道。则乌在其天人一理耶。大抵理为主宰一言。老兄谨守先训。无复疑贰。何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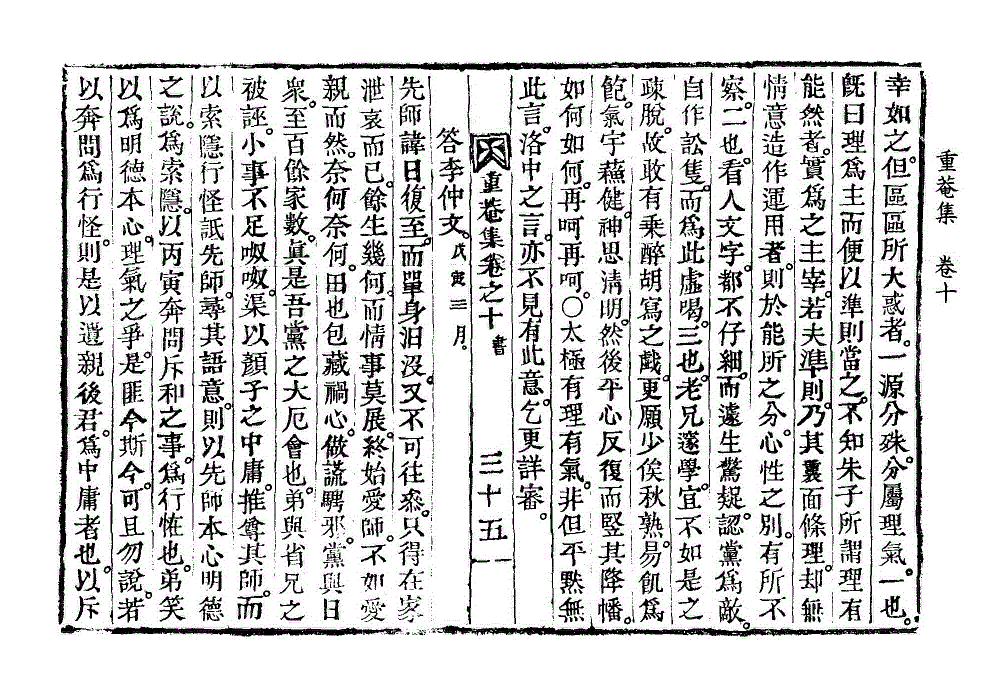 幸如之。但区区所大惑者。一源分殊。分属理气。一也。既曰理为主而便以准则当之。不知朱子所谓理有能然者。实为之主宰。若夫准则。乃其里面条理。却无情意造作运用者。则于能所之分。心性之别。有所不察。二也。看人文字。都不仔细。而遽生惊疑。认党为敌。自作讼只。而为此虚喝。三也。老兄邃学。宜不如是之疏脱。故敢有乘醉胡写之戏。更愿少俟秋熟。易饥为饱。气宇苏健。神思清明。然后平心反复而竖其降幡。如何如何。再呵再呵。○太极有理有气。非但平默无此言。洛中之言。亦不见有此意。乞更详审。
幸如之。但区区所大惑者。一源分殊。分属理气。一也。既曰理为主而便以准则当之。不知朱子所谓理有能然者。实为之主宰。若夫准则。乃其里面条理。却无情意造作运用者。则于能所之分。心性之别。有所不察。二也。看人文字。都不仔细。而遽生惊疑。认党为敌。自作讼只。而为此虚喝。三也。老兄邃学。宜不如是之疏脱。故敢有乘醉胡写之戏。更愿少俟秋熟。易饥为饱。气宇苏健。神思清明。然后平心反复而竖其降幡。如何如何。再呵再呵。○太极有理有气。非但平默无此言。洛中之言。亦不见有此意。乞更详审。答李仲文。(戊寅三月。)
先师讳日复至。而单身汩没。又不可往参。只得在家泄哀而已。馀生几何。而情事莫展。终始爱师。不如爱亲而然。奈何奈何。田也包藏祸心。做谎骋邪。党与日众。至百馀家数。真是吾党之大厄会也。弟与省兄之被诬。小事不足呶呶。渠以颜子之中庸。推尊其师。而以索隐行怪诋先师。寻其语意。则以先师本心明德之说。为索隐。以丙寅奔问斥和之事。为行怪也。弟笑以为明德本心。理气之争。是匪今斯今。可且勿说。若以奔问为行怪。则是以遗亲后君。为中庸者也。以斥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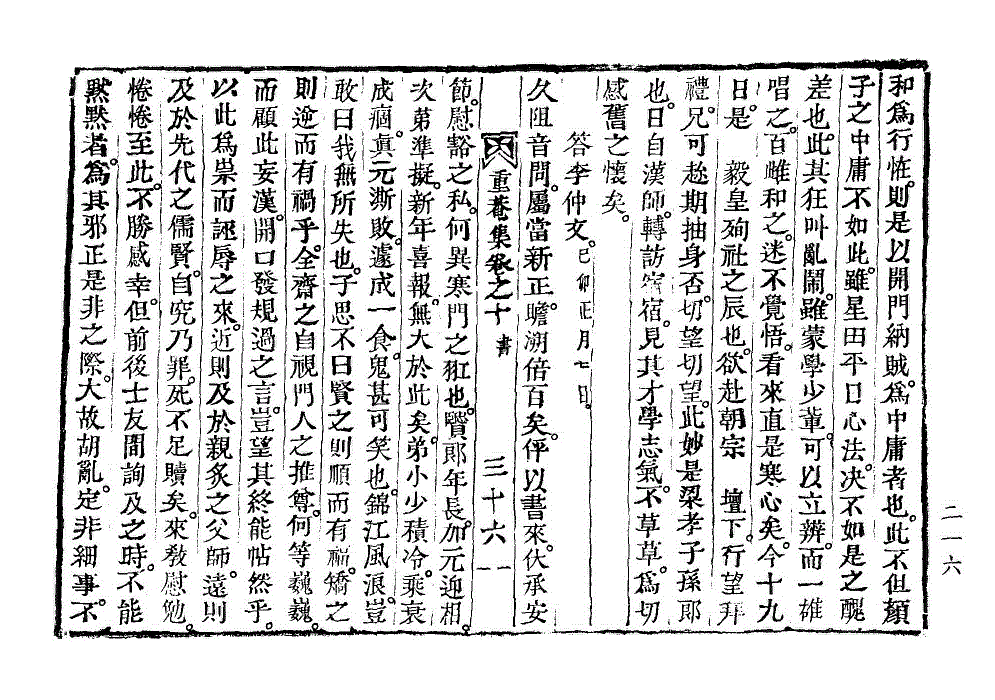 和为行怪。则是以开门纳贼。为中庸者也。此不但颜子之中庸不如此。虽星田平日心法。决不如是之丑差也。此其狂叫乱闹。虽蒙学少辈。可以立辨。而一雄唱之。百雌和之。迷不觉悟。看来直是寒心矣。今十九日。是 毅皇殉社之辰也。欲赴朝宗 坛下。行望拜礼。兄可趁期抽身否。切望切望。此妙是梁孝子孙郎也。日自汉师。转访宿宿。见其才学志气。不草草。为切感旧之怀矣。
和为行怪。则是以开门纳贼。为中庸者也。此不但颜子之中庸不如此。虽星田平日心法。决不如是之丑差也。此其狂叫乱闹。虽蒙学少辈。可以立辨。而一雄唱之。百雌和之。迷不觉悟。看来直是寒心矣。今十九日。是 毅皇殉社之辰也。欲赴朝宗 坛下。行望拜礼。兄可趁期抽身否。切望切望。此妙是梁孝子孙郎也。日自汉师。转访宿宿。见其才学志气。不草草。为切感旧之怀矣。答李仲文。(己卯正月七日。)
久阻音问。属当新正。瞻溯倍百矣。伻以书来。伏承安节。慰豁之私。何异寒门之羾也。贤郎年长。加元迎相。次第准拟。新年喜报。无大于此矣。弟小少积冷。乘衰成痼。真元澌败。遽成一食。鬼甚可笑也。锦江风浪。岂敢曰我无所失也。子思不曰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乎。全斋之自视门人之推尊。何等巍巍。而顾此妄汉。开口发规过之言。岂望其终能帖然乎。以此为祟而诬辱之来。近则及于亲炙之父师。远则及于先代之儒贤。自究乃罪。死不足赎矣。来教慰勉。惓惓至此。不胜感幸。但前后士友间询及之时。不能默默者。为其邪正是非之际。大故胡乱。定非细事。不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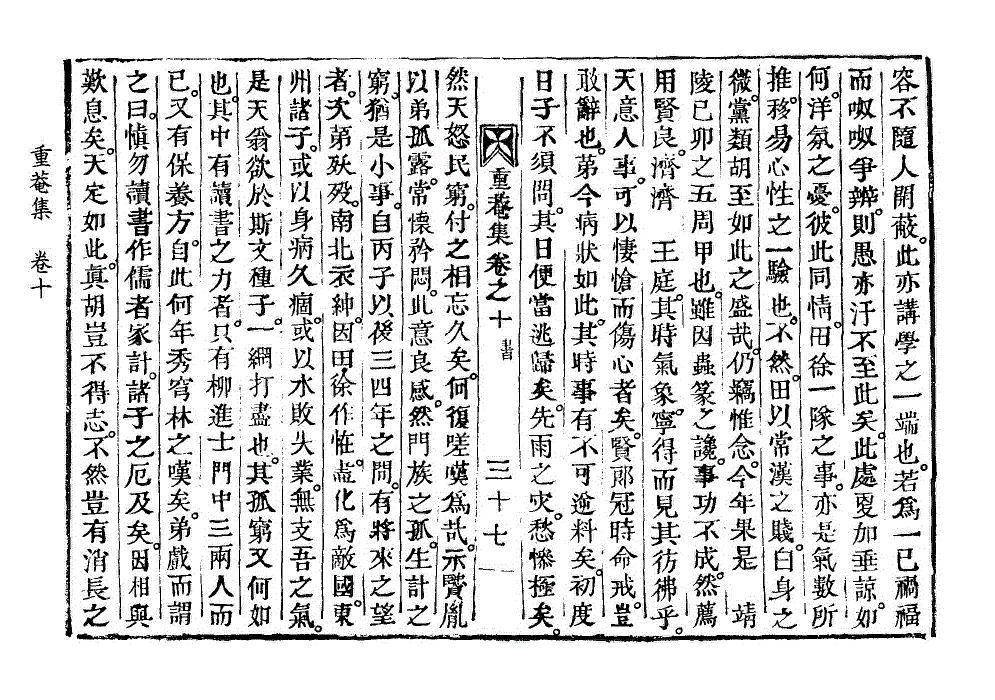 容不随人开蔽。此亦讲学之一端也。若为一己祸福而呶呶争辨。则愚亦污不至此矣。此处更加垂谅。如何。洋氛之忧。彼此同情。田徐一队之事。亦是气数所推。移易心性之一验也。不然。田以常汉之贱。白身之微。党类胡至如此之盛哉。仍窃惟念。今年果是 靖陵己卯之五周甲也。虽因虫篆之谗。事功不成。然荐用贤良。济济 王庭。其时气象。宁得而见其彷佛乎。天意人事。可以悽怆而伤心者矣。贤郎冠时命戒。岂敢辞也。第今病状如此。其时事有不可逆料矣。初度日子不须问。其日便当逃归矣。先雨之灾。愁惨极矣。然天怒民穷。付之相忘久矣。何复嗟叹为哉。示贤胤以弟孤露。常怀矜闷。此意良感。然门族之孤。生计之穷。犹是小事。自丙子以后三四年之间。有将来之望者。次第夭殁。南北衣绅。因田,徐作怪。尽化为敌国。东州诸子。或以身病久痼。或以水败失业。无支吾之气。是天翁欲于斯文种子。一网打尽也。其孤穷又何如也。其中有读书之力者。只有柳进士门中三两人而已。又有保养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之叹矣。弟戏而谓之曰。慎勿读书作儒者家计。诸子之厄及矣。因相与叹息矣。天定如此。真胡岂不得志。不然岂有消长之
容不随人开蔽。此亦讲学之一端也。若为一己祸福而呶呶争辨。则愚亦污不至此矣。此处更加垂谅。如何。洋氛之忧。彼此同情。田徐一队之事。亦是气数所推。移易心性之一验也。不然。田以常汉之贱。白身之微。党类胡至如此之盛哉。仍窃惟念。今年果是 靖陵己卯之五周甲也。虽因虫篆之谗。事功不成。然荐用贤良。济济 王庭。其时气象。宁得而见其彷佛乎。天意人事。可以悽怆而伤心者矣。贤郎冠时命戒。岂敢辞也。第今病状如此。其时事有不可逆料矣。初度日子不须问。其日便当逃归矣。先雨之灾。愁惨极矣。然天怒民穷。付之相忘久矣。何复嗟叹为哉。示贤胤以弟孤露。常怀矜闷。此意良感。然门族之孤。生计之穷。犹是小事。自丙子以后三四年之间。有将来之望者。次第夭殁。南北衣绅。因田,徐作怪。尽化为敌国。东州诸子。或以身病久痼。或以水败失业。无支吾之气。是天翁欲于斯文种子。一网打尽也。其孤穷又何如也。其中有读书之力者。只有柳进士门中三两人而已。又有保养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之叹矣。弟戏而谓之曰。慎勿读书作儒者家计。诸子之厄及矣。因相与叹息矣。天定如此。真胡岂不得志。不然岂有消长之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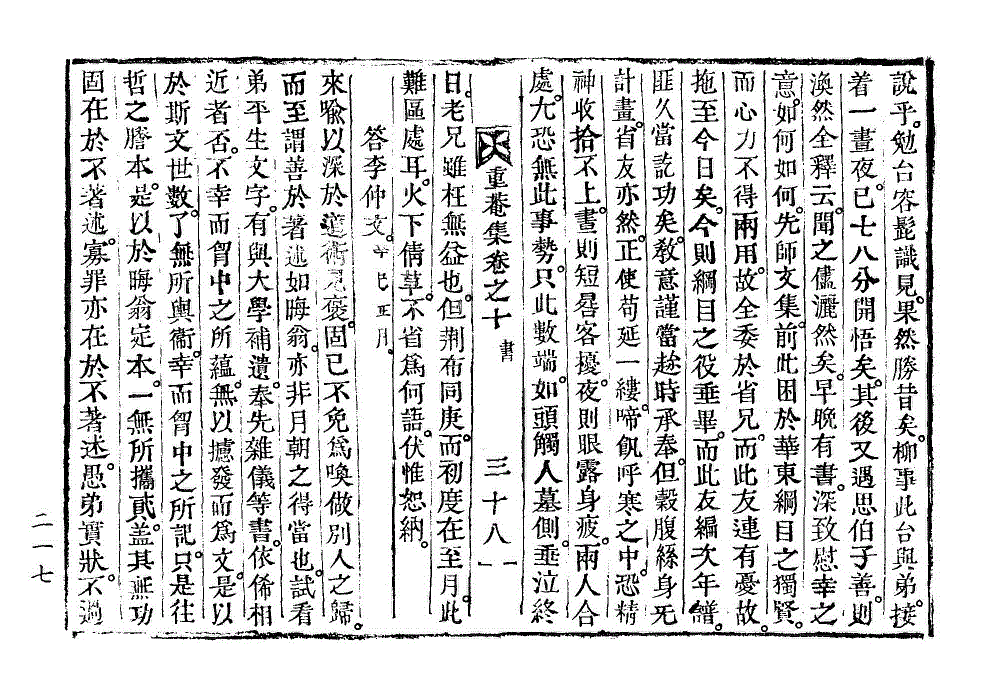 说乎。勉台容髭识见。果然胜昔矣。柳事此台与弟。接着一昼夜。已七八分开悟矣。其后又遇思伯子善。则涣然全释云。闻之尽洒然矣。早晚有书。深致慰幸之意。如何如何。先师文集。前此困于华东纲目之独贤。而心力不得两用。故全委于省兄。而此友连有忧故。拖至今日矣。今则纲目之役垂毕。而此友编次年谱。匪久当讫功矣。教意谨当趁时承奉。但谷腹丝身无计画。省友亦然。正使苟延一缕。啼饥呼寒之中。恐精神收拾不上。昼则短晷客扰。夜则眼露身疲。两人合处。尤恐无此事势。只此数端。如头触人墓侧。垂泣终日。老兄虽枉无益也。但荆布同庚。而初度在至月。此难区处耳。火下倩草。不省为何语。伏惟恕纳。
说乎。勉台容髭识见。果然胜昔矣。柳事此台与弟。接着一昼夜。已七八分开悟矣。其后又遇思伯子善。则涣然全释云。闻之尽洒然矣。早晚有书。深致慰幸之意。如何如何。先师文集。前此困于华东纲目之独贤。而心力不得两用。故全委于省兄。而此友连有忧故。拖至今日矣。今则纲目之役垂毕。而此友编次年谱。匪久当讫功矣。教意谨当趁时承奉。但谷腹丝身无计画。省友亦然。正使苟延一缕。啼饥呼寒之中。恐精神收拾不上。昼则短晷客扰。夜则眼露身疲。两人合处。尤恐无此事势。只此数端。如头触人墓侧。垂泣终日。老兄虽枉无益也。但荆布同庚。而初度在至月。此难区处耳。火下倩草。不省为何语。伏惟恕纳。答李仲文。(辛巳正月。)
来喻以深于道术见褒。固已不免为唤做别人之归。而至谓善于著述如晦翁。亦非月朝之得当也。试看弟平生文字。有与大学补遗。奉先杂仪等书。依俙相近者否。不幸而胸中之所蕴。无以摅发而为文。是以于斯文世数。了无所舆卫。幸而胸中之所记。只是往哲之誊本。是以于晦翁定本。一无所携贰。盖其无功固在于不著述。寡罪亦在于不著迷。愚弟实状。不过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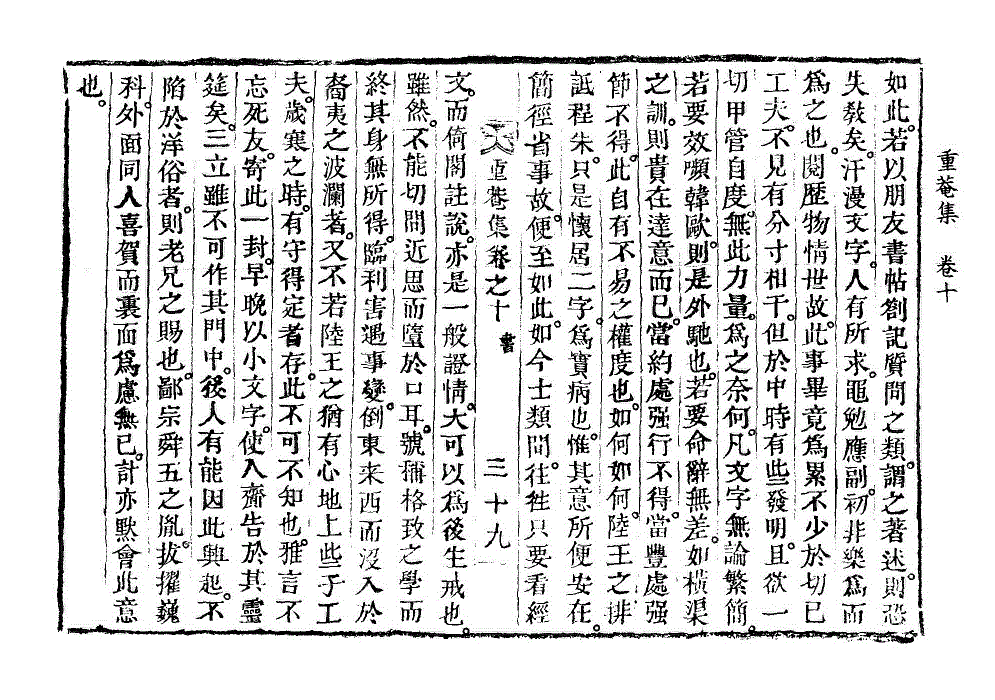 如此。若以朋友书帖劄记质问之类。谓之著述。则恐失教矣。汗漫文字。人有所求。黾勉应副。初非乐为而为之也。阅历物情世故。此事毕竟为累不少于切己工夫。不见有分寸相干。但于中时有些发明。且欲一切甲管自度。无此力量。为之奈何。凡文字无论繁简。若要效嚬韩欧。则是外驰也。若要命辞无差。如横渠之训。则贵在达意而已。当约处强行不得。当丰处强节不得。此自有不易之权度也。如何如何。陆王之排诋程朱。只是怀居二字。为实病也。惟其意所便安在。简径省事故。便至如此。如今士类间。往往只要看经文。而倚阁注说。亦是一般證情。大可以为后生戒也。虽然。不能切问近思而堕于口耳。号称格致之学而终其身无所得。临利害遇事变。倒东来西而没入于裔夷之波澜者。又不若陆王之犹有心地上些子工夫。岁寒之时。有守得定者存。此不可不知也。雅言不忘死友。寄此一封。早晚以小文字。使入赍告于其灵筵矣。三立虽不可作其门中。后人有能因此兴起。不陷于洋俗者。则老见之赐也。鄙宗舜五之胤。拔擢巍科。外面同人喜贺而里面为虑无已。计亦默会此意也。
如此。若以朋友书帖劄记质问之类。谓之著述。则恐失教矣。汗漫文字。人有所求。黾勉应副。初非乐为而为之也。阅历物情世故。此事毕竟为累不少于切己工夫。不见有分寸相干。但于中时有些发明。且欲一切甲管自度。无此力量。为之奈何。凡文字无论繁简。若要效嚬韩欧。则是外驰也。若要命辞无差。如横渠之训。则贵在达意而已。当约处强行不得。当丰处强节不得。此自有不易之权度也。如何如何。陆王之排诋程朱。只是怀居二字。为实病也。惟其意所便安在。简径省事故。便至如此。如今士类间。往往只要看经文。而倚阁注说。亦是一般證情。大可以为后生戒也。虽然。不能切问近思而堕于口耳。号称格致之学而终其身无所得。临利害遇事变。倒东来西而没入于裔夷之波澜者。又不若陆王之犹有心地上些子工夫。岁寒之时。有守得定者存。此不可不知也。雅言不忘死友。寄此一封。早晚以小文字。使入赍告于其灵筵矣。三立虽不可作其门中。后人有能因此兴起。不陷于洋俗者。则老见之赐也。鄙宗舜五之胤。拔擢巍科。外面同人喜贺而里面为虑无已。计亦默会此意也。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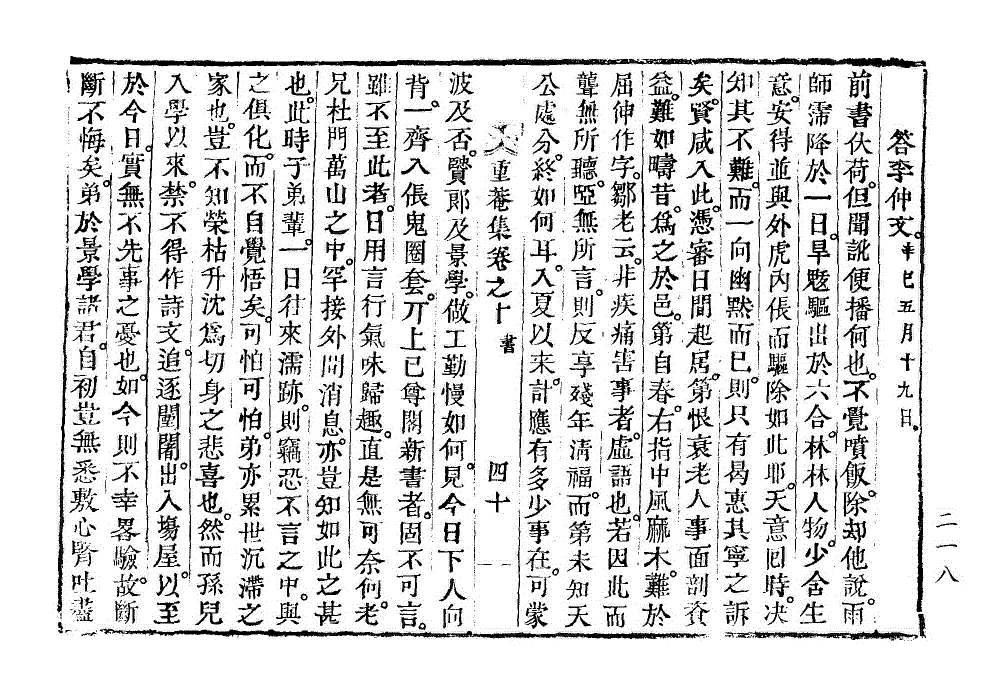 答李仲文。(辛巳五月十九日。)
答李仲文。(辛巳五月十九日。)前书伏荷。但闻讹便播何也。不觉喷饭。除却他说。雨师霈降于一日。旱魃驱出于六合。林林人物。少含生意。安得并与外虎内伥而驱除如此耶。天意回时。决知其不难。而一向幽默而已。则只有曷惠其宁之诉矣。贤咸入此。凭审日间起居。第恨衰老人事面剖资益。难如畴昔。为之于邑。第自春。右指中风麻木。难于屈伸作字。邹老云。非疾痛害事者。虚语也。若因此而聋无所听。哑无所言。则反享残年清福。而第未知天公处分。终如何耳。入夏以来。计应有多少事在。可蒙波及否。贤郎及景学。做工勤慢如何。见今日下人向背。一齐入伥鬼圈套。丌上已尊阁新书者。固不可言。虽不至此者。日用言行气味归趣。直是无可奈何。老兄杜门万山之中。罕接外间消息。亦岂知如此之甚也。此时子弟辈。一日往来濡迹。则窃恐不言之中。与之俱化。而不自觉悟矣。可怕可怕。弟亦累世沉滞之家也。岂不知荣枯升沈为切身之悲喜也。然而孙儿入学以来。禁不得作诗文。追逐闉阇。出入场屋。以至于今日。实无不先事之忧也。如今则不幸略验。故断断不悔矣。弟于景学诸君。自初岂无悉敷心肾吐尽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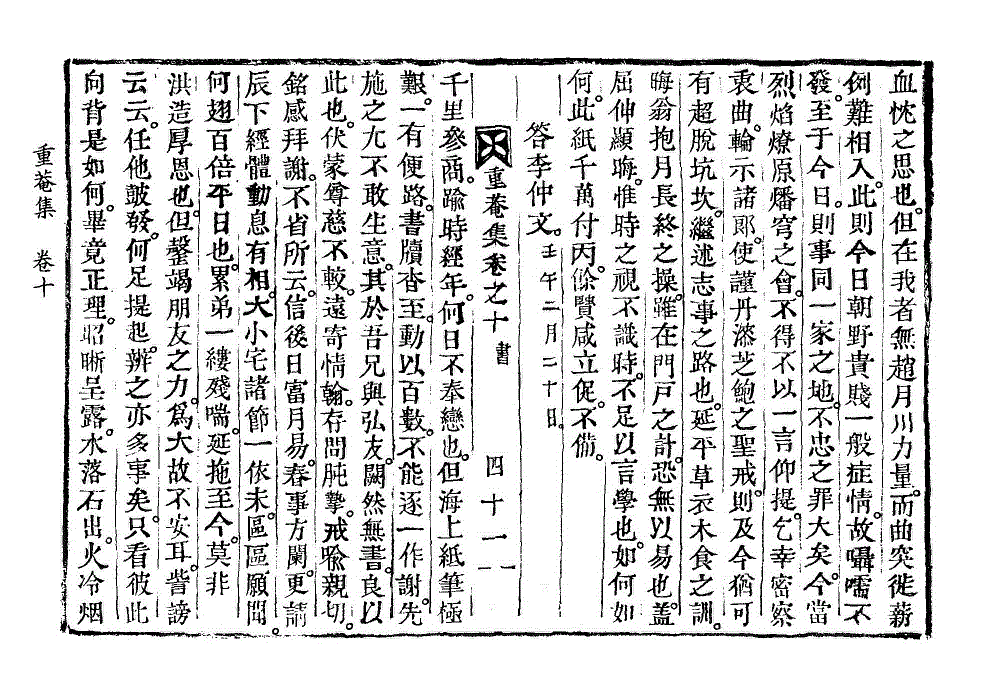 血忱之思也。但在我者无赵月川力量。而曲突徙薪例难相入。此则今日朝野贵贱一般症情。故嗫嚅不发。至于今日。则事同一家之地。不忠之罪大矣。今当烈焰燎原燔穹之会。不得不以一言仰提。乞幸密察衷曲。轮示诸郎。使谨丹漆芝鲍之圣戒。则及今犹可有超脱坑坎。继述志事之路也。延平草衣木食之训。晦翁抱月长终之操。虽在门户之计。恐无以易也。盖屈伸显晦。惟时之视不识时。不足以言学也。如何如何。此纸千万付丙。馀贤咸立促。不备。
血忱之思也。但在我者无赵月川力量。而曲突徙薪例难相入。此则今日朝野贵贱一般症情。故嗫嚅不发。至于今日。则事同一家之地。不忠之罪大矣。今当烈焰燎原燔穹之会。不得不以一言仰提。乞幸密察衷曲。轮示诸郎。使谨丹漆芝鲍之圣戒。则及今犹可有超脱坑坎。继述志事之路也。延平草衣木食之训。晦翁抱月长终之操。虽在门户之计。恐无以易也。盖屈伸显晦。惟时之视不识时。不足以言学也。如何如何。此纸千万付丙。馀贤咸立促。不备。答李仲文。(壬午二月二十日。)
千里参商。踰时经年。何日不奉恋也。但海上纸笔极艰。一有便路。书牍杳至。动以百数。不能逐一作谢。先施之尤不敢生意。其于吾兄与弘友。阙然无书。良以此也。伏蒙尊慈不较。远寄情翰。存问肫挚。戒喻亲切。铭感拜谢。不省所云。信后日富月易。春事方阑。更请辰下经体动息有相。大小宅诸节一依未。区区愿闻。何翅百倍平日也。累弟一缕残喘。延拖至今。莫非 洪造厚恩也。但罄竭朋友之力。为大故不安耳。訾谤云云。任他鼓发。何足提起。辨之亦多事矣。只看彼此向背是如何。毕竟正理。昭晰呈露。水落石出。火冷烟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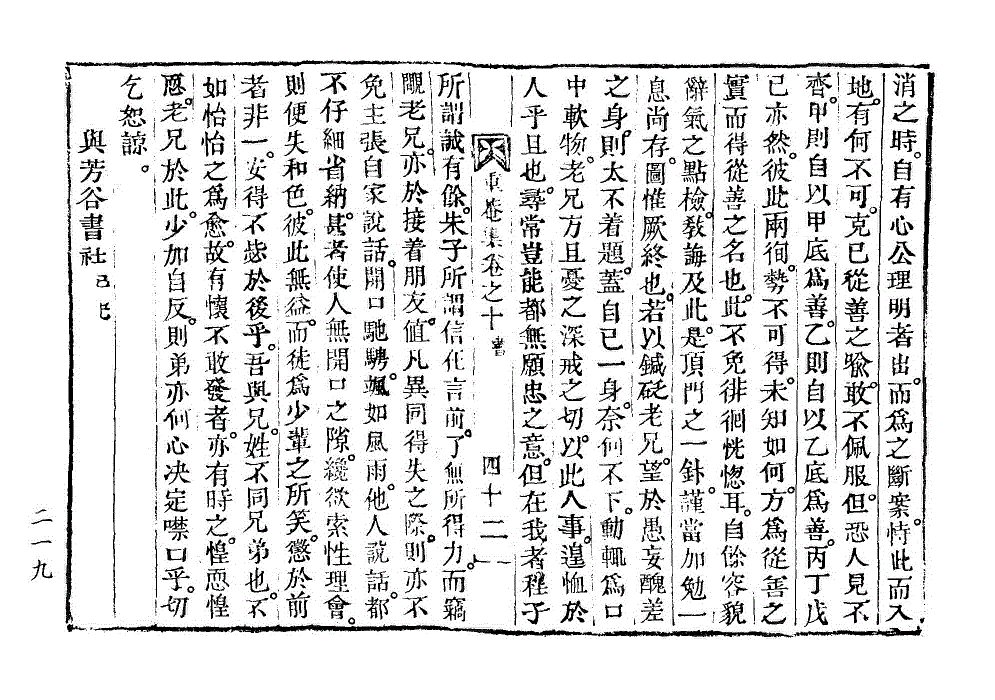 消之时。自有心公理明者出。而为之断案。恃此而入地。有何不可。克己从善之喻。敢不佩服。但恐人见不齐。甲则自以甲底为善。乙则自以乙底为善。丙丁戊己亦然。彼此两徇。势不可得。未知如何。方为从善之实而得从善之名也。此不免徘徊恍惚耳。自馀容貌辞气之点检。教诲及此。是顶门之一针。谨当加勉一息尚存。图惟厥终也。若以针砭老兄。望于愚妄丑差之身。则太不着题。盖自己一身。奈何不下。动辄为口中软物。老兄方且忧之深戒之切。以此人事。遑恤于人乎且也。寻常岂能都无愿忠之意。但在我者程子所谓诚有馀。朱子所谓信任言前。了无所得力。而窃覸老兄。亦于接着朋友。值凡异同得失之际。则亦不免主张自家说话。开口驰骋。飒如风雨。他人说话。都不仔细省纳。甚者使人无开口之隙。才欲索性理会。则便失和色。彼此无益。而徒为少辈之所笑。惩于前者非一。安得不毖于后乎。吾与兄。姓不同兄弟也。不如怡怡之为愈。故有怀不敢发者。亦有时之。惶恧惶恧。老兄于此。少加自反。则弟亦何心决定噤口乎。切乞恕谅。
消之时。自有心公理明者出。而为之断案。恃此而入地。有何不可。克己从善之喻。敢不佩服。但恐人见不齐。甲则自以甲底为善。乙则自以乙底为善。丙丁戊己亦然。彼此两徇。势不可得。未知如何。方为从善之实而得从善之名也。此不免徘徊恍惚耳。自馀容貌辞气之点检。教诲及此。是顶门之一针。谨当加勉一息尚存。图惟厥终也。若以针砭老兄。望于愚妄丑差之身。则太不着题。盖自己一身。奈何不下。动辄为口中软物。老兄方且忧之深戒之切。以此人事。遑恤于人乎且也。寻常岂能都无愿忠之意。但在我者程子所谓诚有馀。朱子所谓信任言前。了无所得力。而窃覸老兄。亦于接着朋友。值凡异同得失之际。则亦不免主张自家说话。开口驰骋。飒如风雨。他人说话。都不仔细省纳。甚者使人无开口之隙。才欲索性理会。则便失和色。彼此无益。而徒为少辈之所笑。惩于前者非一。安得不毖于后乎。吾与兄。姓不同兄弟也。不如怡怡之为愈。故有怀不敢发者。亦有时之。惶恧惶恧。老兄于此。少加自反。则弟亦何心决定噤口乎。切乞恕谅。与芳谷书社(己巳)
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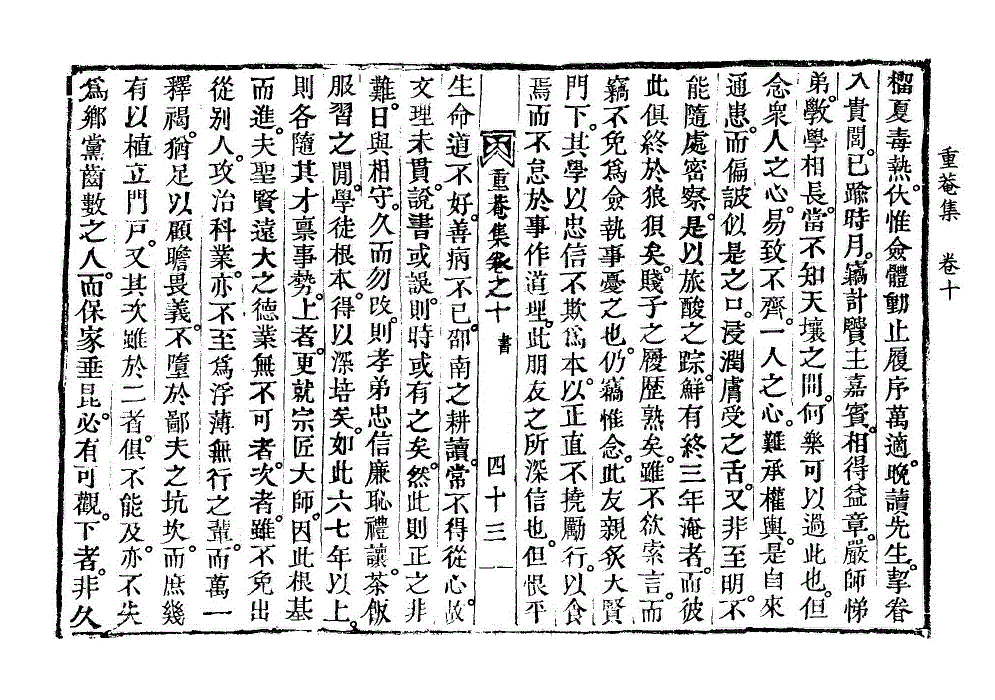 榴夏毒热。伏惟佥体动止履序万适。晚读先生。挈眷入贵闾。已踰时月。窃计贤主嘉宾。相得益章。严师悌弟。敩学相长。当不知天壤之间。何乐可以过此也。但念众人之心。易致不齐。一人之心。难承权舆。是自来通患。而偏诐似是之口。浸润肤受之舌。又非至明。不能随处密察。是以旅酸之踪。鲜有终三年淹者。而彼此俱终于狼狈矣。贱子之履历熟矣。虽不欲索言。而窃不免为佥执事忧之也。仍窃惟念。此友亲炙大贤门下。其学以忠信不欺为本。以正直不挠励行。以食焉而不怠于事作道埋。此朋友之所深信也。但恨平生命道不好。善病不已。邵南之耕读。常不得从心。故文理未贯。说书或误。则时或有之矣。然此则正之非难。日与相守。久而勿改。则孝弟忠信廉耻礼让。茶饭服习之閒。学徒根本。得以深培矣。如此六七年以上。则各随其才禀事势。上者。更就宗匠大师。因此根基而进。夫圣贤远大之德业无不可者。次者。虽不免出从别人。攻治科业。亦不至为浮薄无行之辈。而万一释褐。犹足以顾瞻畏义。不堕于鄙夫之境坎。而庶几有以植立门户。又其次虽于二者。俱不能及。亦不失为乡党齿数之人。而保家垂昆。必有可观。下者。非久
榴夏毒热。伏惟佥体动止履序万适。晚读先生。挈眷入贵闾。已踰时月。窃计贤主嘉宾。相得益章。严师悌弟。敩学相长。当不知天壤之间。何乐可以过此也。但念众人之心。易致不齐。一人之心。难承权舆。是自来通患。而偏诐似是之口。浸润肤受之舌。又非至明。不能随处密察。是以旅酸之踪。鲜有终三年淹者。而彼此俱终于狼狈矣。贱子之履历熟矣。虽不欲索言。而窃不免为佥执事忧之也。仍窃惟念。此友亲炙大贤门下。其学以忠信不欺为本。以正直不挠励行。以食焉而不怠于事作道埋。此朋友之所深信也。但恨平生命道不好。善病不已。邵南之耕读。常不得从心。故文理未贯。说书或误。则时或有之矣。然此则正之非难。日与相守。久而勿改。则孝弟忠信廉耻礼让。茶饭服习之閒。学徒根本。得以深培矣。如此六七年以上。则各随其才禀事势。上者。更就宗匠大师。因此根基而进。夫圣贤远大之德业无不可者。次者。虽不免出从别人。攻治科业。亦不至为浮薄无行之辈。而万一释褐。犹足以顾瞻畏义。不堕于鄙夫之境坎。而庶几有以植立门户。又其次虽于二者。俱不能及。亦不失为乡党齿数之人。而保家垂昆。必有可观。下者。非久重庵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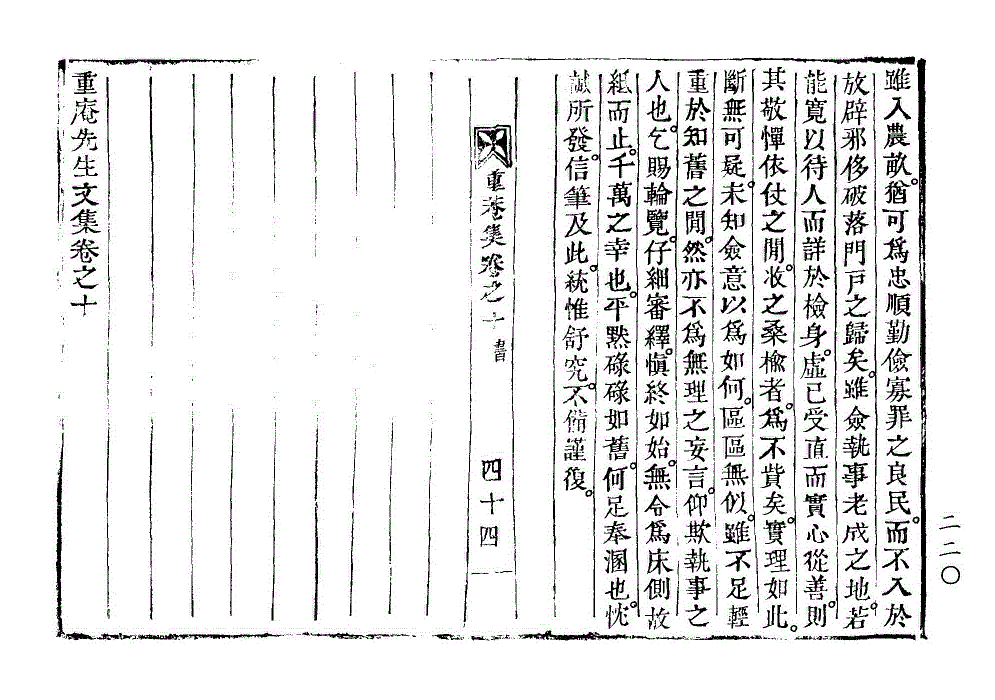 虽入农亩。犹可为忠顺勤俭寡罪之良民。而不入于放辟邪侈破落门户之归矣。虽佥执事老成之地。若能宽以待人而详于检身。虚己受直而实心从善。则其敬惮依仗之閒。收之桑榆者。为不赀矣。实理如此。断无可疑。未知佥意以为如何。区区无似。虽不足轻重于知旧之閒。然亦不为无理之妄言。仰欺执事之人也。乞赐轮览。仔细审绎。慎终如始。无令为床侧故纸而止。千万之幸也。平默碌碌如旧。何足奉溷也。忱诚所发。信笔及此。统惟舒究。不备谨复。
虽入农亩。犹可为忠顺勤俭寡罪之良民。而不入于放辟邪侈破落门户之归矣。虽佥执事老成之地。若能宽以待人而详于检身。虚己受直而实心从善。则其敬惮依仗之閒。收之桑榆者。为不赀矣。实理如此。断无可疑。未知佥意以为如何。区区无似。虽不足轻重于知旧之閒。然亦不为无理之妄言。仰欺执事之人也。乞赐轮览。仔细审绎。慎终如始。无令为床侧故纸而止。千万之幸也。平默碌碌如旧。何足奉溷也。忱诚所发。信笔及此。统惟舒究。不备谨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