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x 页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杂著
杂著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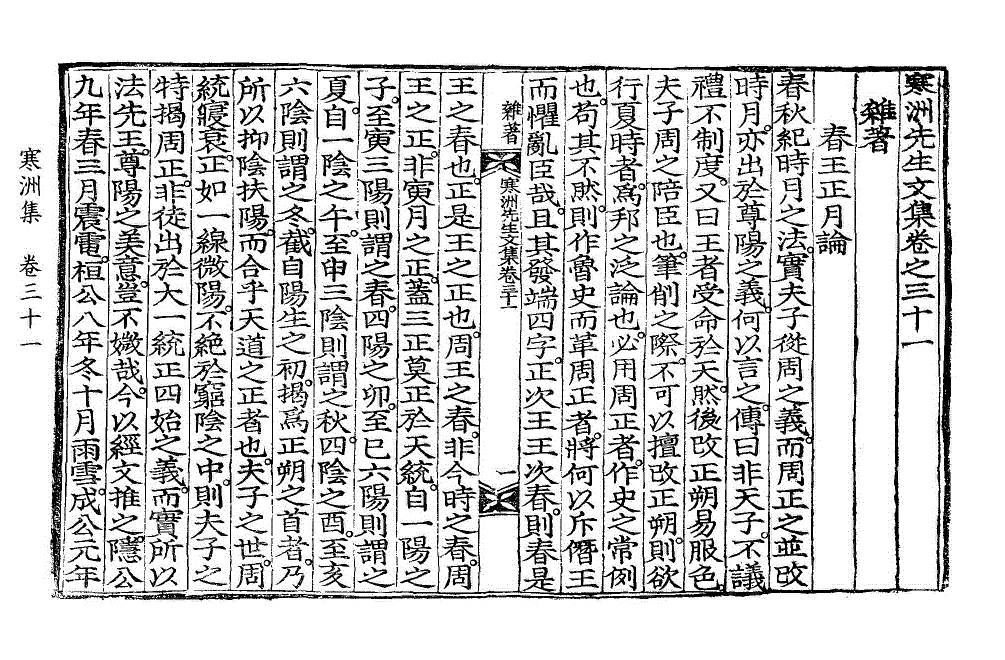 春王正月论
春王正月论春秋纪时月之法。实夫子从周之义。而周正之并改时月。亦出于尊阳之义。何以言之。传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又曰王者受命于天。然后改正朔易服色。夫子周之陪臣也。笔削之际。不可以擅改正朔。则欲行夏时者。为邦之泛论也。必用周正者。作史之常例也。苟其不然。则作鲁史而革周正者。将何以斥僭王而惧乱臣哉。且其发端四字。正次王王次春。则春是王之春也。正是王之正也。周王之春。非今时之春。周王之正。非寅月之正。盖三正莫正于天统。自一阳之子。至寅三阳则谓之春。四阳之卯。至已六阳则谓之夏。自一阴之午。至申三阴则谓之秋。四阴之酉。至亥六阴则谓之冬。截自阳生之初。揭为正朔之首者。乃所以抑阴扶阳。而合乎天道之正者也。夫子之世。周统寝衰。正如一线微阳。不绝于穷阴之中。则夫子之特揭周正。非徒出于大一统正四始之义。而实所以法先王。尊阳之美意。岂不美哉。今以经文推之。隐公九年春三月震电。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成公元年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5L 页
 春二月无冰。夫以夏时言之。则三月之电十月之雪二月之无冰。自是常事。不足为灾。而其实则正月之电八月之雪而十二月而无冰也。所以书之为灾。至若庄公七年。书秋无麦。此以五月为秋也。成公十六年冬。书大有年。此以九月为冬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书陨霜不杀草。此亦十月之事也。若左氏之传则有曰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登观台书云物。直以冬至之日。特揭春王之正。此又事实之大彰明较著者也。且以佗书證之。邹夫子之书曰岁十二月桥梁成。朱子释之为夏正十月。杂记载孟献子之书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日至乃冬至之别名。而正月即建子之月也。汉律历志武王伐纣之岁正月朔。粤五日乙未冬至。而泰誓书之为十有三年春。则此又旁照之无疑者也。独其可疑者。商以建丑为地统。而伊训书之为元祀十有二月。则前乎周而商人之不改月明矣。汉以建亥为岁首。而纲目书之为元年冬十月。则后乎周而汉史之不改时亦明矣。然商书自商书。汉史自汉史。周家所以改时月之常规。新一代之耳目者。何足怪乎。诗人之纪时。与此不叶。如小雅之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豳风之七月
春二月无冰。夫以夏时言之。则三月之电十月之雪二月之无冰。自是常事。不足为灾。而其实则正月之电八月之雪而十二月而无冰也。所以书之为灾。至若庄公七年。书秋无麦。此以五月为秋也。成公十六年冬。书大有年。此以九月为冬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书陨霜不杀草。此亦十月之事也。若左氏之传则有曰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登观台书云物。直以冬至之日。特揭春王之正。此又事实之大彰明较著者也。且以佗书證之。邹夫子之书曰岁十二月桥梁成。朱子释之为夏正十月。杂记载孟献子之书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日至乃冬至之别名。而正月即建子之月也。汉律历志武王伐纣之岁正月朔。粤五日乙未冬至。而泰誓书之为十有三年春。则此又旁照之无疑者也。独其可疑者。商以建丑为地统。而伊训书之为元祀十有二月。则前乎周而商人之不改月明矣。汉以建亥为岁首。而纲目书之为元年冬十月。则后乎周而汉史之不改时亦明矣。然商书自商书。汉史自汉史。周家所以改时月之常规。新一代之耳目者。何足怪乎。诗人之纪时。与此不叶。如小雅之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豳风之七月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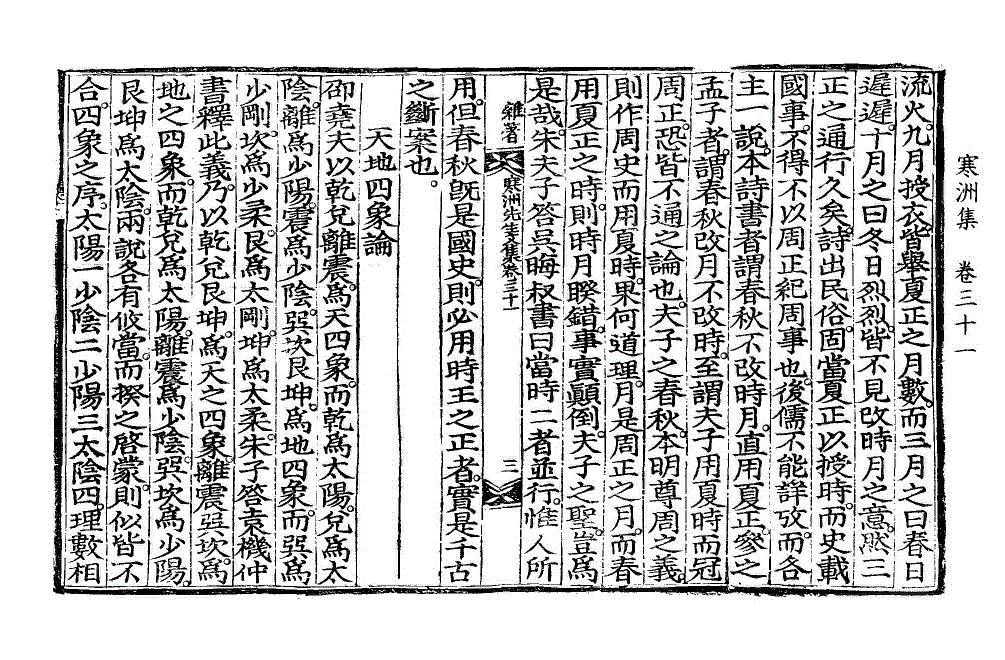 流火。九月授衣。皆举夏正之月数。而三月之曰春日迟迟。十月之曰冬日烈烈。皆不见改时月之意。然三正之通行久矣。诗出民俗。固当夏正以授时。而史载国事。不得不以周正纪周事也。后儒不能详考。而各主一说。本诗书者谓春秋不改时月。直用夏正。参之孟子者。谓春秋改月不改时。至谓夫子用夏时而冠周正。恐皆不通之论也。夫子之春秋。本明尊周之义。则作周史而用夏时。果何道理。月是周正之月。而春用夏正之时。则时月睽错。事实颠倒。夫子之圣。岂为是哉。朱夫子答吴晦叔书曰当时二者并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者。实是千古之断案也。
流火。九月授衣。皆举夏正之月数。而三月之曰春日迟迟。十月之曰冬日烈烈。皆不见改时月之意。然三正之通行久矣。诗出民俗。固当夏正以授时。而史载国事。不得不以周正纪周事也。后儒不能详考。而各主一说。本诗书者谓春秋不改时月。直用夏正。参之孟子者。谓春秋改月不改时。至谓夫子用夏时而冠周正。恐皆不通之论也。夫子之春秋。本明尊周之义。则作周史而用夏时。果何道理。月是周正之月。而春用夏正之时。则时月睽错。事实颠倒。夫子之圣。岂为是哉。朱夫子答吴晦叔书曰当时二者并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者。实是千古之断案也。天地四象论
邵尧夫以乾兑离震。为天四象。而乾为太阳。兑为太阴。离为少阳。震为少阴。巽次艮坤。为地四象。而巽为少刚。坎为少柔。艮为太刚。坤为太柔。朱子答袁机仲书释此义。乃以乾兑艮坤。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为地之四象。而乾兑为太阳。离震为少阴。巽坎为少阳。艮坤为太阴。两说各有攸当。而揆之启蒙。则似皆不合。四象之序。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理数相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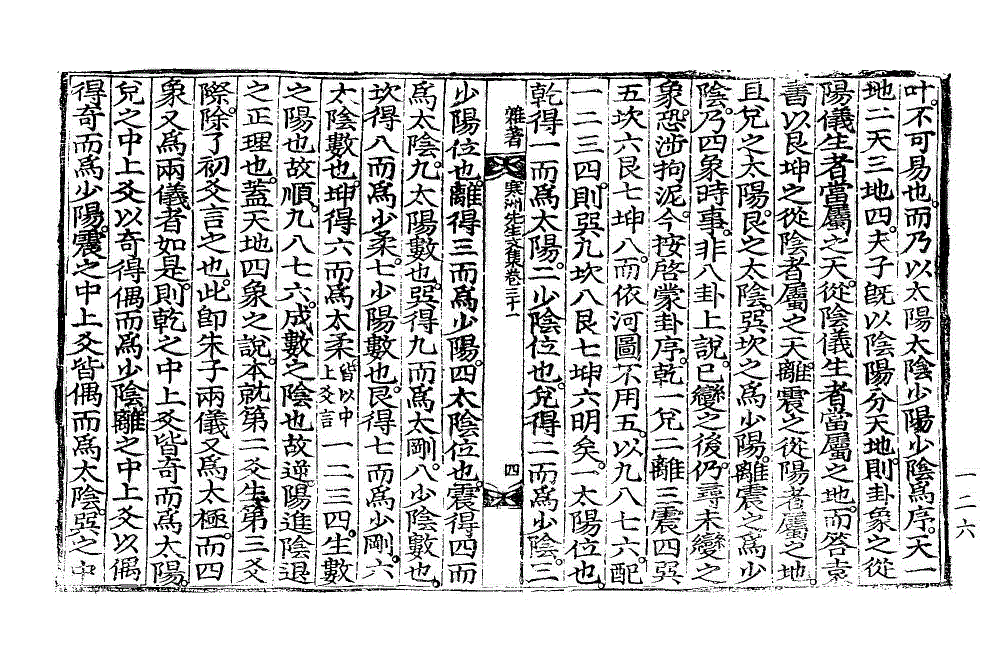 叶。不可易也。而乃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为序。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夫子既以阴阳分天地。则卦象之从阳仪生者当属之天。从阴仪生者当属之地。而答袁书以艮坤之从阴者属之天。离震之从阳者属之地。且兑之太阳。艮之太阴。巽坎之为少阳。离震之为少阴。乃四象时事。非八卦上说。已变之后。仍寻未变之象。恐涉拘泥。今按启蒙卦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依河图不用五。以九八七六。配一二三四。则巽九坎八艮七坤六明矣。一太阳位也。乾得一而为太阳。二少阴位也。兑得二而为少阴。三少阳位也。离得三而为少阳。四太阴位也。震得四而为太阴。九太阳数也。巽得九而为太刚。八少阴数也。坎得八而为少柔。七少阳数也。艮得七而为少刚。六太阴数也。坤得六而为太柔。(皆以中上爻言)一二三四。生数之阳也故顺。九八七六。成数之阴也故逆。阳进阴退之正理也。盖天地四象之说。本就第二爻生第三爻际。除了初爻言之也。此即朱子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者如是。则乾之中上爻皆奇而为太阳。兑之中上爻以奇得偶而为少阴。离之中上爻以偶得奇而为少阳。震之中上爻皆偶而为太阴。巽之中
叶。不可易也。而乃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为序。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夫子既以阴阳分天地。则卦象之从阳仪生者当属之天。从阴仪生者当属之地。而答袁书以艮坤之从阴者属之天。离震之从阳者属之地。且兑之太阳。艮之太阴。巽坎之为少阳。离震之为少阴。乃四象时事。非八卦上说。已变之后。仍寻未变之象。恐涉拘泥。今按启蒙卦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依河图不用五。以九八七六。配一二三四。则巽九坎八艮七坤六明矣。一太阳位也。乾得一而为太阳。二少阴位也。兑得二而为少阴。三少阳位也。离得三而为少阳。四太阴位也。震得四而为太阴。九太阳数也。巽得九而为太刚。八少阴数也。坎得八而为少柔。七少阳数也。艮得七而为少刚。六太阴数也。坤得六而为太柔。(皆以中上爻言)一二三四。生数之阳也故顺。九八七六。成数之阴也故逆。阳进阴退之正理也。盖天地四象之说。本就第二爻生第三爻际。除了初爻言之也。此即朱子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者如是。则乾之中上爻皆奇而为太阳。兑之中上爻以奇得偶而为少阴。离之中上爻以偶得奇而为少阳。震之中上爻皆偶而为太阴。巽之中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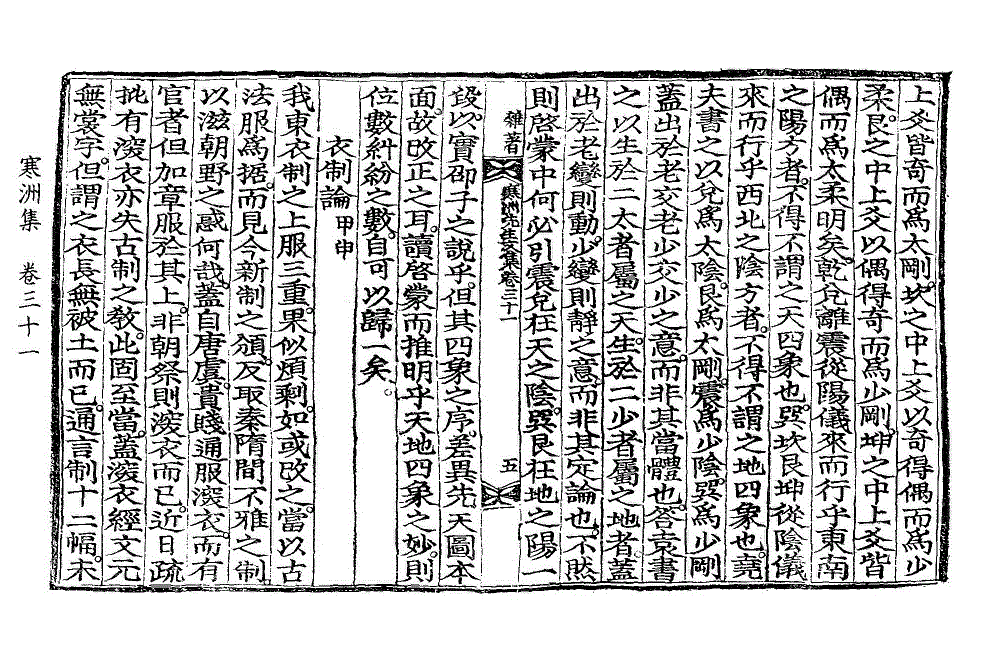 上爻皆奇而为太刚。坎之中上爻以奇得偶而为少柔。艮之中上爻以偶得奇而为少刚。坤之中上爻皆偶而为太柔明矣。乾兑离震从阳仪来而行乎东南之阳方者。不得不谓之天四象也。巽坎艮坤从阴仪来而行乎西北之阴方者。不得不谓之地四象也。尧夫书之以兑为太阴。艮为太刚。震为少阴。巽为少刚。盖出于老交老少交少之意。而非其当体也。答袁书之以生于二太者属之天。生于二少者属之地者。盖出于老变则动。少变则静之意。而非其定论也。不然则启蒙中何必引震兑在天之阴。巽艮在地之阳一段。以实邵子之说乎。但其四象之序。差异先天图本面。故改正之耳。读启蒙而推明乎天地四象之妙。则位数纠纷之数。自可以归一矣。
上爻皆奇而为太刚。坎之中上爻以奇得偶而为少柔。艮之中上爻以偶得奇而为少刚。坤之中上爻皆偶而为太柔明矣。乾兑离震从阳仪来而行乎东南之阳方者。不得不谓之天四象也。巽坎艮坤从阴仪来而行乎西北之阴方者。不得不谓之地四象也。尧夫书之以兑为太阴。艮为太刚。震为少阴。巽为少刚。盖出于老交老少交少之意。而非其当体也。答袁书之以生于二太者属之天。生于二少者属之地者。盖出于老变则动。少变则静之意。而非其定论也。不然则启蒙中何必引震兑在天之阴。巽艮在地之阳一段。以实邵子之说乎。但其四象之序。差异先天图本面。故改正之耳。读启蒙而推明乎天地四象之妙。则位数纠纷之数。自可以归一矣。衣制论(甲申)
我东衣制之上服三重。果似烦剩。如或改之。当以古法服为据。而见今新制之颁。反取秦隋间不雅之制。以滋朝野之惑何哉。盖自唐虞。贯贱通服深衣。而有官者但加章服于其上。非朝祭则深衣而已。近日疏批有深衣亦失古制之教。此固至当。盖深衣经文元无裳字。但谓之衣长无被土而已。通言制十二幅。未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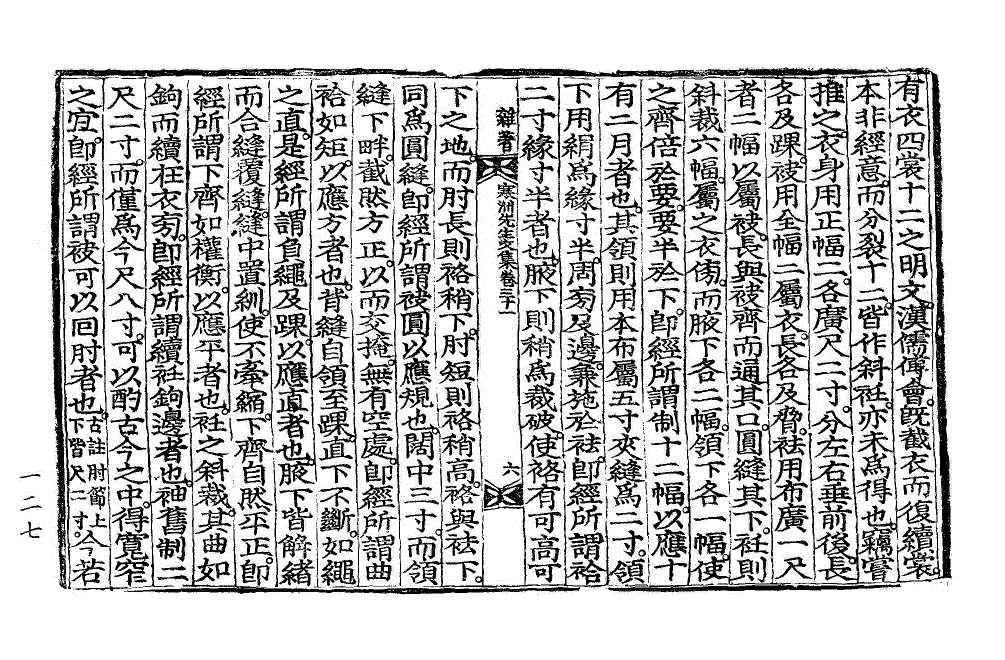 有衣四裳十二之明文。汉儒傅会。既截衣而复续裳。本非经意。而分裂十二。皆作斜衽。亦未为得也。窃尝推之。衣身用正幅二。各广尺二寸。分左右垂前后。长各及踝。袂用全幅二属衣。长各及胁。袪用布广一尺者二幅以属袂。长与袂齐而通其口。圆缝其下。衽则斜裁六幅。属之衣傍。而腋下各二幅。领下各一幅。使之齐倍于要。要半于下。即经所谓制十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者也。其领则用本布属五寸夹缝为二寸。领下用绢为缘寸半。周旁及边。兼施于袪。即经所谓袷二寸缘寸半者也。腋下则稍为裁破。使袼有可高可下之地。而肘长则袼稍下。肘短则袼稍高。袼与袪下。同为圆缝。即经所谓袂圆以应规也。阔中三寸。而领缝下畔。截然方正。以而交掩。无有空处。即经所谓曲袷如矩。以应方者也。背缝自领至踝。直下不断。如绳之直。是经所谓负绳及踝。以应直者也。腋下皆解绪而合缝覆缝。缝中置紃。使不牵缩。下齐自然平正。即经所谓下齐如权衡。以应平者也。衽之斜裁。其曲如钩而续在衣旁。即经所谓续衽钩边者也。袖旧制二尺二寸。而仅为今尺八寸。可以酌古今之中。得宽窄之宜。即经所谓袂可以回肘者也。(古注肘节上下皆尺二寸。)今若
有衣四裳十二之明文。汉儒傅会。既截衣而复续裳。本非经意。而分裂十二。皆作斜衽。亦未为得也。窃尝推之。衣身用正幅二。各广尺二寸。分左右垂前后。长各及踝。袂用全幅二属衣。长各及胁。袪用布广一尺者二幅以属袂。长与袂齐而通其口。圆缝其下。衽则斜裁六幅。属之衣傍。而腋下各二幅。领下各一幅。使之齐倍于要。要半于下。即经所谓制十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者也。其领则用本布属五寸夹缝为二寸。领下用绢为缘寸半。周旁及边。兼施于袪。即经所谓袷二寸缘寸半者也。腋下则稍为裁破。使袼有可高可下之地。而肘长则袼稍下。肘短则袼稍高。袼与袪下。同为圆缝。即经所谓袂圆以应规也。阔中三寸。而领缝下畔。截然方正。以而交掩。无有空处。即经所谓曲袷如矩。以应方者也。背缝自领至踝。直下不断。如绳之直。是经所谓负绳及踝。以应直者也。腋下皆解绪而合缝覆缝。缝中置紃。使不牵缩。下齐自然平正。即经所谓下齐如权衡。以应平者也。衽之斜裁。其曲如钩而续在衣旁。即经所谓续衽钩边者也。袖旧制二尺二寸。而仅为今尺八寸。可以酌古今之中。得宽窄之宜。即经所谓袂可以回肘者也。(古注肘节上下皆尺二寸。)今若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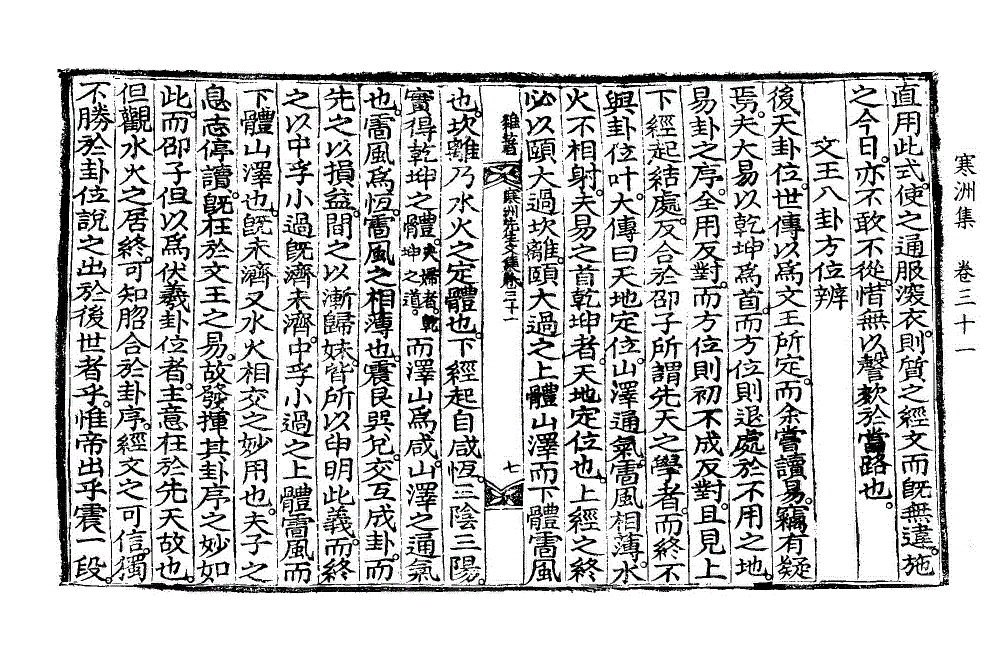 直用此式。使之通服深衣。则质之经文而既无违。施之今日。亦不敢不从。惜无以謦欬于当路也。
直用此式。使之通服深衣。则质之经文而既无违。施之今日。亦不敢不从。惜无以謦欬于当路也。文王八卦方位辨
后天卦位。世传以为文王所定。而余尝读易。窃有疑焉。夫大易以乾坤为首。而方位则退处于不用之地。易卦之序。全用反对。而方位则初不成反对。且见上下经起结处。反合于邵子所谓先天之学者。而终不与卦位叶。大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䨓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夫易之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上经之终必以颐大过坎离。颐大过之上体山泽而下体䨓风也。坎离乃水火之定体也。下经起自咸恒。三阴三阳。实得乾坤之体。(夫妇者。乾坤之道。)而泽山为咸。山泽之通气也。䨓风为恒。䨓风之相薄也。震艮巽兑。交互成卦。而先之以损益。间之以渐归妹。皆所以申明此义。而终之以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中孚小过之上体䨓风而下体山泽也。既未济又水火相交之妙用也。夫子之息志停读。既在于文王之易。故发挥其卦序之妙如此。而邵子但以为伏羲卦位者。主意在于先天故也。但观水火之居终。可知吻合于卦序。经文之可信。独不胜于卦位说之出于后世者乎。惟帝出乎震一段。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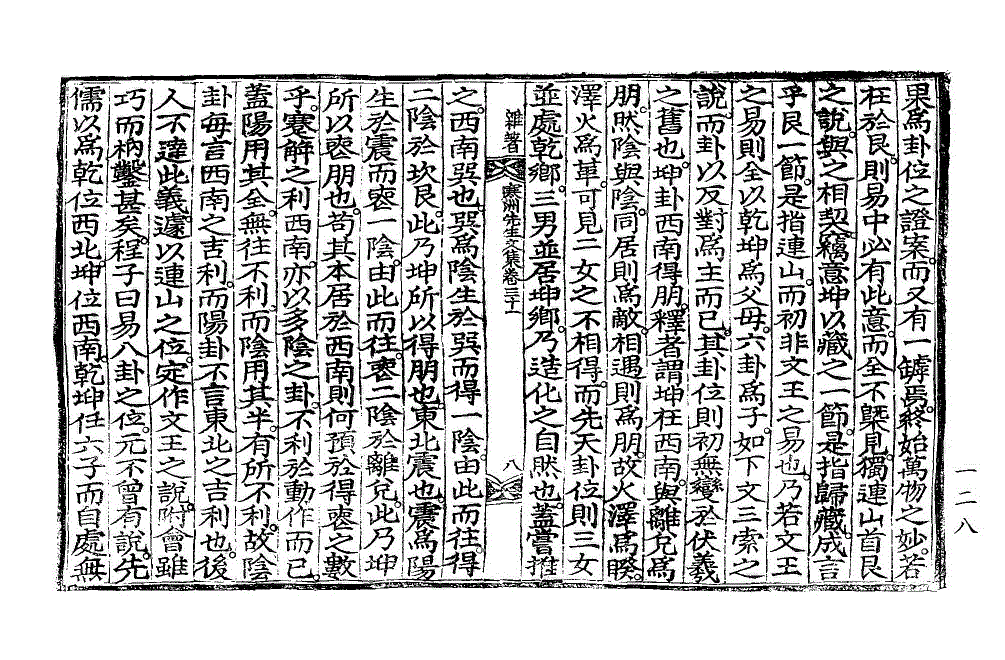 果为卦位之證案。而又有一罅焉。终始万物之妙。若在于艮。则易中必有此意。而全不槩见。独连山首艮之说。与之相契。窃意坤以藏之一节。是指归藏。成言乎艮一节。是指连山。而初非文王之易也。乃若文王之易则全以乾坤为父母。六卦为子。如下文三索之说。而卦以反对为主而已。其卦位则初无变于伏羲之旧也。坤卦西南得朋。释者谓坤在西南。与离兑为朋。然阴与阴。同居则为敌。相遇则为朋。故火泽为睽。泽火为革。可见二女之不相得。而先天卦位则三女并处乾乡。三男并居坤乡。乃造化之自然也。盖尝推之。西南巽也。巽为阴生于巽而得一阴。由此而往。得二阴于坎艮。此乃坤所以得朋也。东北震也。震为阳生于震而丧一阴。由此而往。丧二阴于离兑。此乃坤所以丧朋也。苟其本居于西南则何预于得丧之数乎。蹇解之利西南。亦以多阴之卦。不利于动作而已。盖阳用其全。无往不利。而阴用其半。有所不利。故阴卦每言西南之吉利。而阳卦不言东北之吉利也。后人不达此义。遽以连山之位。定作文王之说。附会虽巧而枘凿甚矣。程子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说。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处无
果为卦位之證案。而又有一罅焉。终始万物之妙。若在于艮。则易中必有此意。而全不槩见。独连山首艮之说。与之相契。窃意坤以藏之一节。是指归藏。成言乎艮一节。是指连山。而初非文王之易也。乃若文王之易则全以乾坤为父母。六卦为子。如下文三索之说。而卦以反对为主而已。其卦位则初无变于伏羲之旧也。坤卦西南得朋。释者谓坤在西南。与离兑为朋。然阴与阴。同居则为敌。相遇则为朋。故火泽为睽。泽火为革。可见二女之不相得。而先天卦位则三女并处乾乡。三男并居坤乡。乃造化之自然也。盖尝推之。西南巽也。巽为阴生于巽而得一阴。由此而往。得二阴于坎艮。此乃坤所以得朋也。东北震也。震为阳生于震而丧一阴。由此而往。丧二阴于离兑。此乃坤所以丧朋也。苟其本居于西南则何预于得丧之数乎。蹇解之利西南。亦以多阴之卦。不利于动作而已。盖阳用其全。无往不利。而阴用其半。有所不利。故阴卦每言西南之吉利。而阳卦不言东北之吉利也。后人不达此义。遽以连山之位。定作文王之说。附会虽巧而枘凿甚矣。程子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说。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处无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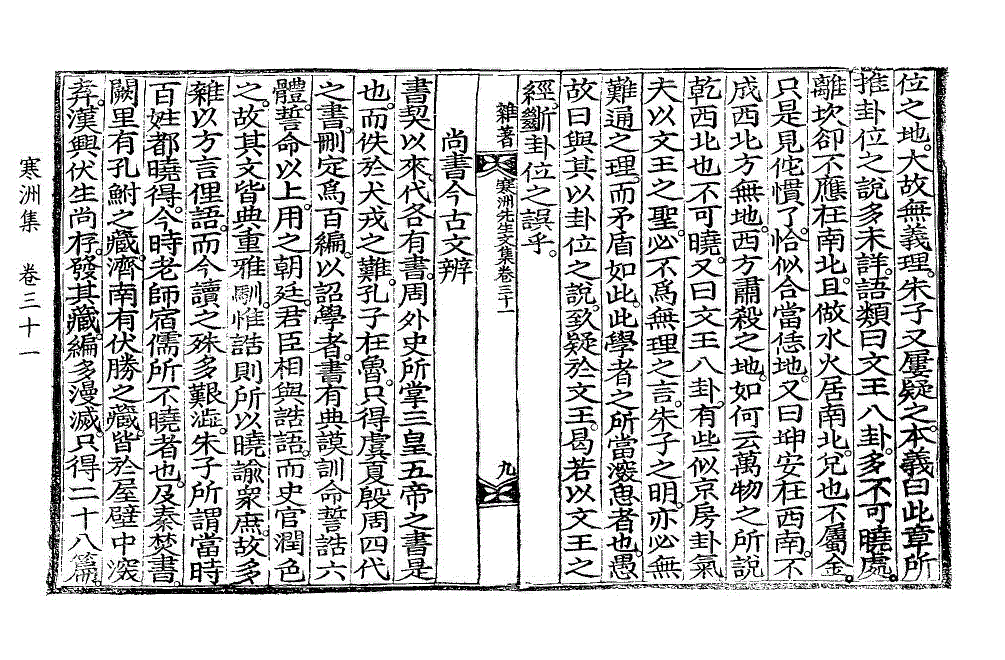 位之地。大故无义理。朱子又屡疑之。本义曰此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语类曰文王八卦。多不可晓处。离坎却不应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兑也不属金。只是见佗惯了。恰似合当恁地。又曰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云万物之所说乾西北也不可晓。又曰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气夫以文王之圣。必不为无理之言。朱子之明。亦必无难通之理。而矛盾如此。此学者之所当深思者也。愚故曰与其以卦位之说。致疑于文王。曷若以文王之经。断卦位之误乎。
位之地。大故无义理。朱子又屡疑之。本义曰此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语类曰文王八卦。多不可晓处。离坎却不应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兑也不属金。只是见佗惯了。恰似合当恁地。又曰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云万物之所说乾西北也不可晓。又曰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气夫以文王之圣。必不为无理之言。朱子之明。亦必无难通之理。而矛盾如此。此学者之所当深思者也。愚故曰与其以卦位之说。致疑于文王。曷若以文王之经。断卦位之误乎。尚书今古文辨
书契以来。代各有书。周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书是也。而佚于犬戎之难。孔子在鲁。只得虞夏殷周四代之书。删定为百编。以诏学者。书有典谟训命誓诰六体。誓命以上。用之朝廷。君臣相与诰语。而史官润色之。故其文皆典重雅驯。惟诰则所以晓谕众庶。故多杂以方言俚语。而今读之殊多艰涩。朱子所谓当时百姓都晓得。今时老师宿儒所不晓者也。及秦焚书。阙里有孔鲋之藏。济南有伏胜之藏。皆于屋壁中深弆。汉兴伏生尚存。发其藏。编多漫灭。只得二十八篇。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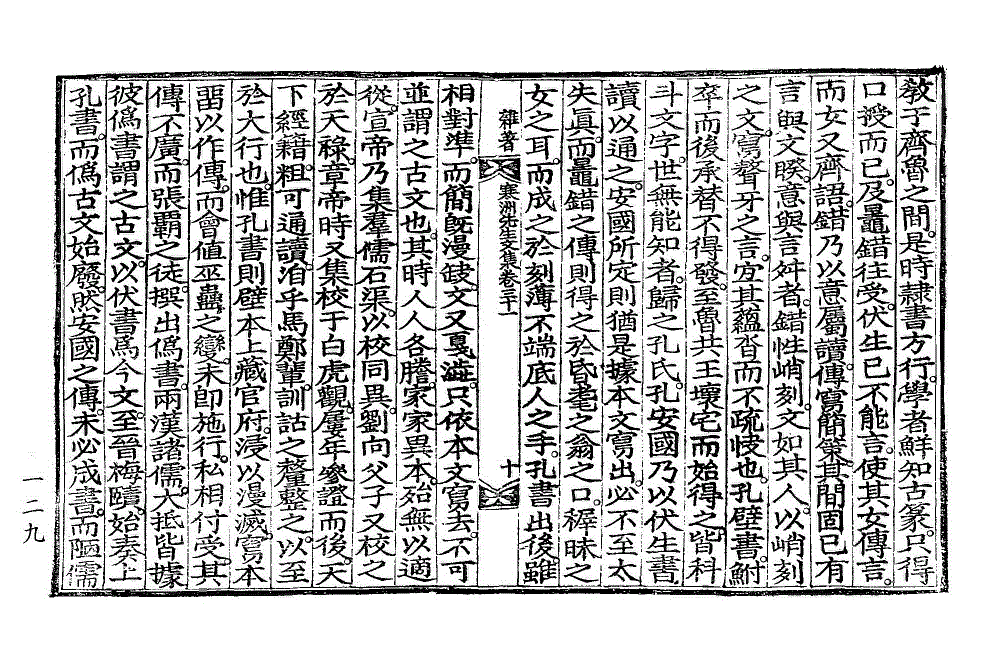 教于齐鲁之间。是时隶书方行。学者鲜知古篆。只得口授而已。及晁错往受。伏生已不能言。使其女传言。而女又齐语。错乃以意属读。传写简策。其间固已有言与文睽。意与言舛者。错性峭刻。文如其人。以峭刻之文。写聱牙之言。宜其蕴沓而不疏快也。孔壁书。鲋卒而后承替不得发。至鲁共王坏宅而始得之。皆科斗文字。世无能知者。归之孔氏。孔安国乃以伏生书读以通之。安国所定则犹是据本文写出。必不至太失真。而晁错之传则得之于昏耄之翁之口。稚昧之女之耳。而成之于刻薄不端底人之手。孔书出后。虽相对准。而简既漫缺。文又戛涩。只依本文写去。不可并谓之古文也。其时人人各誊。家家异本。殆无以适从。宣帝乃集群儒石渠。以校同异。刘向父子又校之于天禄。章帝时又集校于白虎观。屡年参證而后。天下经籍。粗可通读。洎乎马郑辈。训诂之釐整之。以至于大行也。惟孔书则壁本上藏官府。浸以漫灭。写本留以作传。而会值巫蛊之变。未即施行。私相付受。其传不广。而张霸之徒。撰出伪书。两汉诸儒。大抵皆据彼伪书谓之古文。以伏书为今文。至晋梅赜。始奏上孔书。而伪古文始废。然安国之传。未必成书。而陋儒
教于齐鲁之间。是时隶书方行。学者鲜知古篆。只得口授而已。及晁错往受。伏生已不能言。使其女传言。而女又齐语。错乃以意属读。传写简策。其间固已有言与文睽。意与言舛者。错性峭刻。文如其人。以峭刻之文。写聱牙之言。宜其蕴沓而不疏快也。孔壁书。鲋卒而后承替不得发。至鲁共王坏宅而始得之。皆科斗文字。世无能知者。归之孔氏。孔安国乃以伏生书读以通之。安国所定则犹是据本文写出。必不至太失真。而晁错之传则得之于昏耄之翁之口。稚昧之女之耳。而成之于刻薄不端底人之手。孔书出后。虽相对准。而简既漫缺。文又戛涩。只依本文写去。不可并谓之古文也。其时人人各誊。家家异本。殆无以适从。宣帝乃集群儒石渠。以校同异。刘向父子又校之于天禄。章帝时又集校于白虎观。屡年参證而后。天下经籍。粗可通读。洎乎马郑辈。训诂之釐整之。以至于大行也。惟孔书则壁本上藏官府。浸以漫灭。写本留以作传。而会值巫蛊之变。未即施行。私相付受。其传不广。而张霸之徒。撰出伪书。两汉诸儒。大抵皆据彼伪书谓之古文。以伏书为今文。至晋梅赜。始奏上孔书。而伪古文始废。然安国之传。未必成书。而陋儒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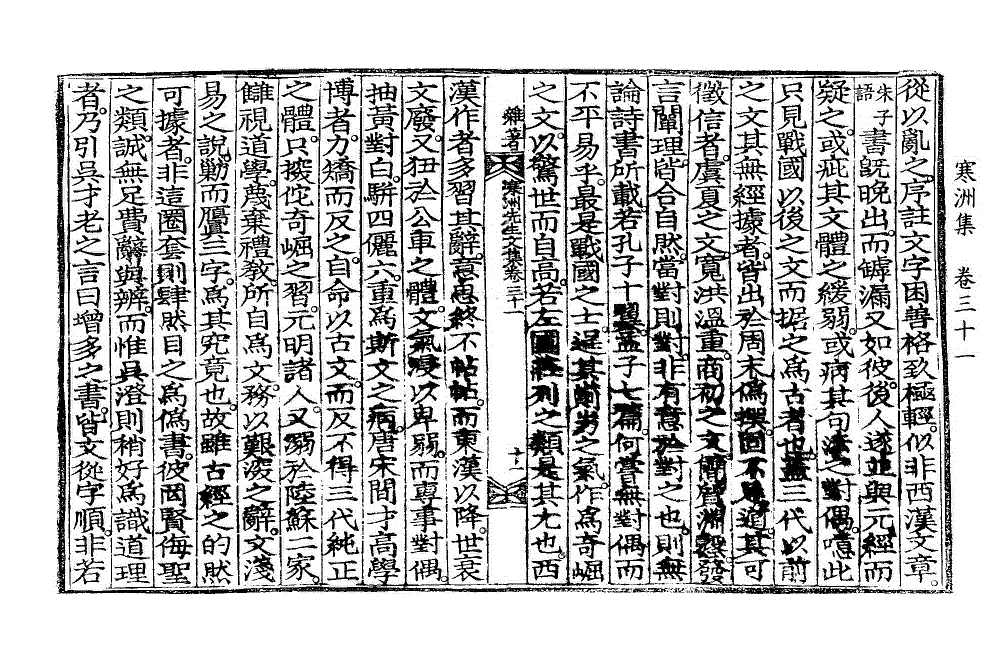 从以乱之。序注文字困善格致极轻。似非西汉文章。(朱子语)书既晚出。而罅漏又如彼。后人遂并与元经而疑之。或疵其文体之缓弱。或病其句法之对偶。噫此只见战国以后之文而据之为古者也。盖三代以前之文其无经据者。皆出于周末伪撰。固不足道。其可徵信者。虞夏之文。宽洪温重。商初之文。简质渊悫。发言阐理。皆合自然。当对则对。非有意于对之也。则无论诗书所载。若孔子十翼。孟子七篇。何尝无对偶而不平易乎。最是战国之士。逞其则屴之气。作为奇崛之文。以惊世而自高。若左国庄列之类是其尤也。西汉作者多习其辞。意思终不帖帖。而东汉以降。世衰文废。又狃于公车之体。文气浸以卑弱。而专事对偶。抽黄对白。骈四俪六。重为斯文之病。唐宋间才高学博者。力矫而反之。自命以古文。而反不得三代纯正之体。只探佗奇崛之习。元明诸人。又溺于陆苏二家。雠视道学。蔑弃礼教。所自为文。务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剿而赝三字。为其究竟也。故虽古经之的然可据者。非这圈套则肆然目之为伪书。彼罔贤侮圣之类。诚无足费辞与辨。而惟吴澄则稍好为识道理者。乃引吴才老之言曰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
从以乱之。序注文字困善格致极轻。似非西汉文章。(朱子语)书既晚出。而罅漏又如彼。后人遂并与元经而疑之。或疵其文体之缓弱。或病其句法之对偶。噫此只见战国以后之文而据之为古者也。盖三代以前之文其无经据者。皆出于周末伪撰。固不足道。其可徵信者。虞夏之文。宽洪温重。商初之文。简质渊悫。发言阐理。皆合自然。当对则对。非有意于对之也。则无论诗书所载。若孔子十翼。孟子七篇。何尝无对偶而不平易乎。最是战国之士。逞其则屴之气。作为奇崛之文。以惊世而自高。若左国庄列之类是其尤也。西汉作者多习其辞。意思终不帖帖。而东汉以降。世衰文废。又狃于公车之体。文气浸以卑弱。而专事对偶。抽黄对白。骈四俪六。重为斯文之病。唐宋间才高学博者。力矫而反之。自命以古文。而反不得三代纯正之体。只探佗奇崛之习。元明诸人。又溺于陆苏二家。雠视道学。蔑弃礼教。所自为文。务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剿而赝三字。为其究竟也。故虽古经之的然可据者。非这圈套则肆然目之为伪书。彼罔贤侮圣之类。诚无足费辞与辨。而惟吴澄则稍好为识道理者。乃引吴才老之言曰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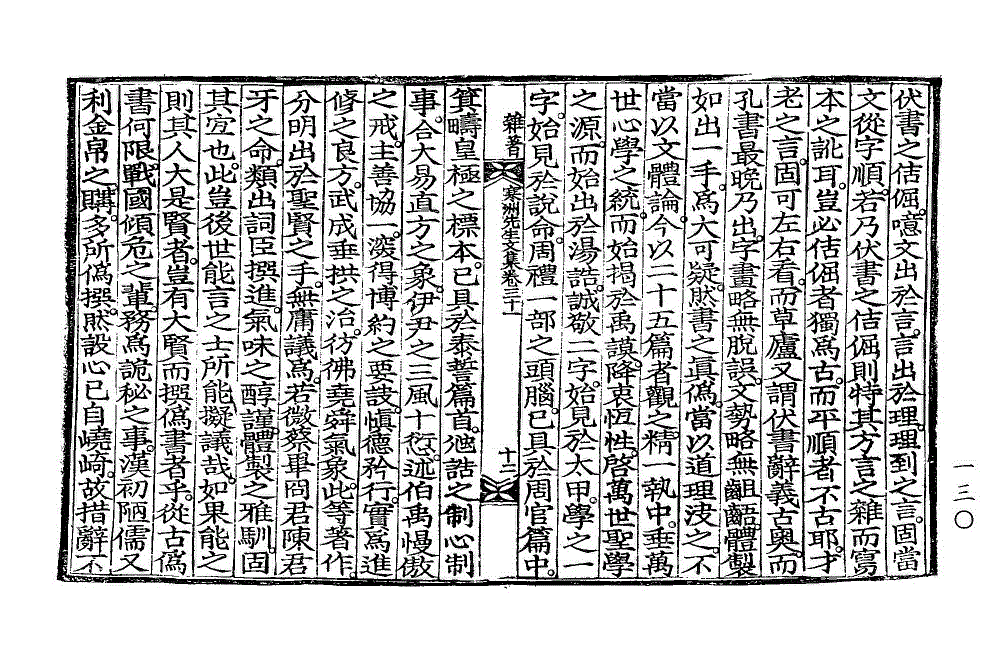 伏书之佶倔。噫文出于言。言出于理。理到之言。固当文从字顺。若乃伏书之佶倔则特其方言之杂而写本之讹耳。岂必佶倔者独为古。而平顺者不古耶。才老之言。固可左右看。而草庐又。谓伏书辞义古奥。而孔书最晚乃出。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体制如出一手。为大可疑。然书之真伪。当以道理决之。不当以文体论。今以二十五篇者观之。精一执中。垂万世心学之统。而始揭于禹谟。降衷恒性。启万世圣学之源。而始出于汤诰。诚敬二字。始见于太甲。学之一字。始见于说命。周礼一部之头脑。已具于周官篇中。箕畴皇极之标本。已具于泰誓篇首。虺诰之制心制事。合大易直方之象。伊尹之三风十愆。述伯禹慢傲之戒。主善协一。深得博约之要诀。慎德矜行。实为进修之良方。武成垂拱之治。彷佛尧舜气象。此等著作。分明出于圣贤之手。无庸议为。若微蔡毕囧君陈君牙之命。类出词臣撰进。气味之醇谨。体制之雅驯。固其宜也。此岂后世能言之士所能拟议哉。如果能之则其人大是贤者。岂有大贤而撰伪书者乎。从古伪书何限。战国倾危之辈。务为诡秘之事。汉初陋儒又利金帛之购。多所伪撰。然设心已自峣崎。故措辞不
伏书之佶倔。噫文出于言。言出于理。理到之言。固当文从字顺。若乃伏书之佶倔则特其方言之杂而写本之讹耳。岂必佶倔者独为古。而平顺者不古耶。才老之言。固可左右看。而草庐又。谓伏书辞义古奥。而孔书最晚乃出。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体制如出一手。为大可疑。然书之真伪。当以道理决之。不当以文体论。今以二十五篇者观之。精一执中。垂万世心学之统。而始揭于禹谟。降衷恒性。启万世圣学之源。而始出于汤诰。诚敬二字。始见于太甲。学之一字。始见于说命。周礼一部之头脑。已具于周官篇中。箕畴皇极之标本。已具于泰誓篇首。虺诰之制心制事。合大易直方之象。伊尹之三风十愆。述伯禹慢傲之戒。主善协一。深得博约之要诀。慎德矜行。实为进修之良方。武成垂拱之治。彷佛尧舜气象。此等著作。分明出于圣贤之手。无庸议为。若微蔡毕囧君陈君牙之命。类出词臣撰进。气味之醇谨。体制之雅驯。固其宜也。此岂后世能言之士所能拟议哉。如果能之则其人大是贤者。岂有大贤而撰伪书者乎。从古伪书何限。战国倾危之辈。务为诡秘之事。汉初陋儒又利金帛之购。多所伪撰。然设心已自峣崎。故措辞不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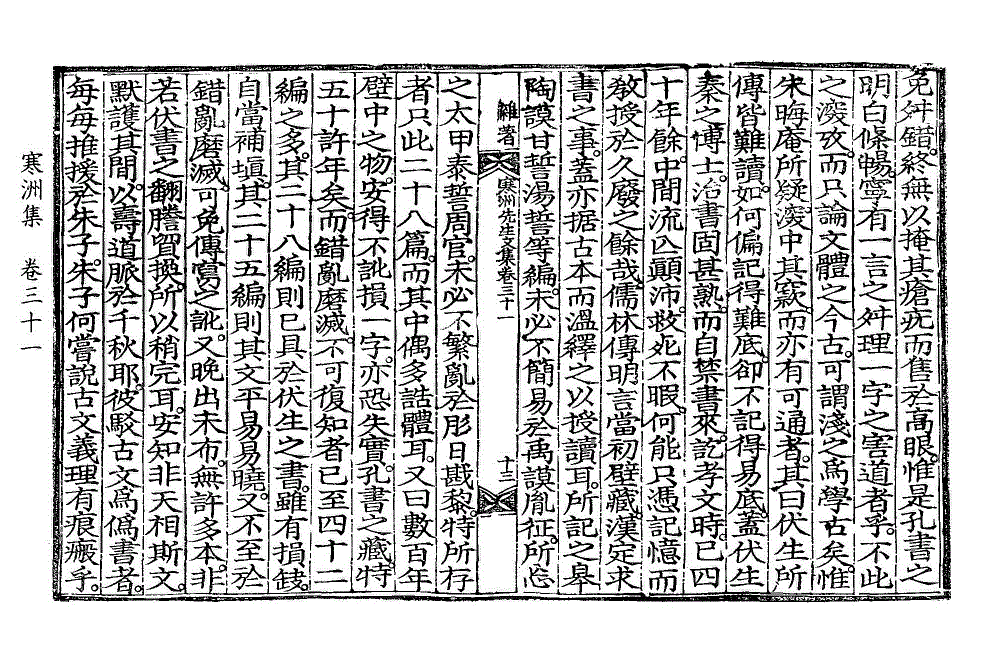 免舛错。终无以掩其疮疣而售于高眼。惟是孔书之明白条畅。宁有一言之舛理一字之害道者乎。不此之深考。而只论文体之今古。可谓浅之为学古矣。惟朱晦庵所疑。深中其窾。而亦有可通者。其曰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盖伏生秦之博士。治书固甚熟。而自禁书来。讫孝文时。已四十年馀。中间流亡颠沛。救死不暇。何能只凭记忆而教授于久废之馀哉。儒林传明言当初壁藏。汉定求书之事。盖亦据古本而温绎之以授读耳。所记之皋陶谟甘誓汤誓等编。未必不简易于禹谟胤征。所忘之太甲泰誓周官。未必不繁乱于肜日戡黎。特所存者只此二十八篇。而其中偶多诰体耳。又曰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亦恐失实。孔书之藏。特五十许年矣。而错乱磨灭。不可复知者已至四十二编之多。其二十八编则已具于伏生之书。虽有损缺。自当补填。其二十五编则其文平易易晓。又不至于错乱磨灭。可免传写之讹。又晚出未布。无许多本。非若伏书之翻誊贸换。所以稍完耳。安知非天相斯文。默护其间。以寿道脉于千秋耶。彼驳古文为伪书者。每每推援于朱子。朱子何尝说古文义理有痕瘢乎。
免舛错。终无以掩其疮疣而售于高眼。惟是孔书之明白条畅。宁有一言之舛理一字之害道者乎。不此之深考。而只论文体之今古。可谓浅之为学古矣。惟朱晦庵所疑。深中其窾。而亦有可通者。其曰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盖伏生秦之博士。治书固甚熟。而自禁书来。讫孝文时。已四十年馀。中间流亡颠沛。救死不暇。何能只凭记忆而教授于久废之馀哉。儒林传明言当初壁藏。汉定求书之事。盖亦据古本而温绎之以授读耳。所记之皋陶谟甘誓汤誓等编。未必不简易于禹谟胤征。所忘之太甲泰誓周官。未必不繁乱于肜日戡黎。特所存者只此二十八篇。而其中偶多诰体耳。又曰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亦恐失实。孔书之藏。特五十许年矣。而错乱磨灭。不可复知者已至四十二编之多。其二十八编则已具于伏生之书。虽有损缺。自当补填。其二十五编则其文平易易晓。又不至于错乱磨灭。可免传写之讹。又晚出未布。无许多本。非若伏书之翻誊贸换。所以稍完耳。安知非天相斯文。默护其间。以寿道脉于千秋耶。彼驳古文为伪书者。每每推援于朱子。朱子何尝说古文义理有痕瘢乎。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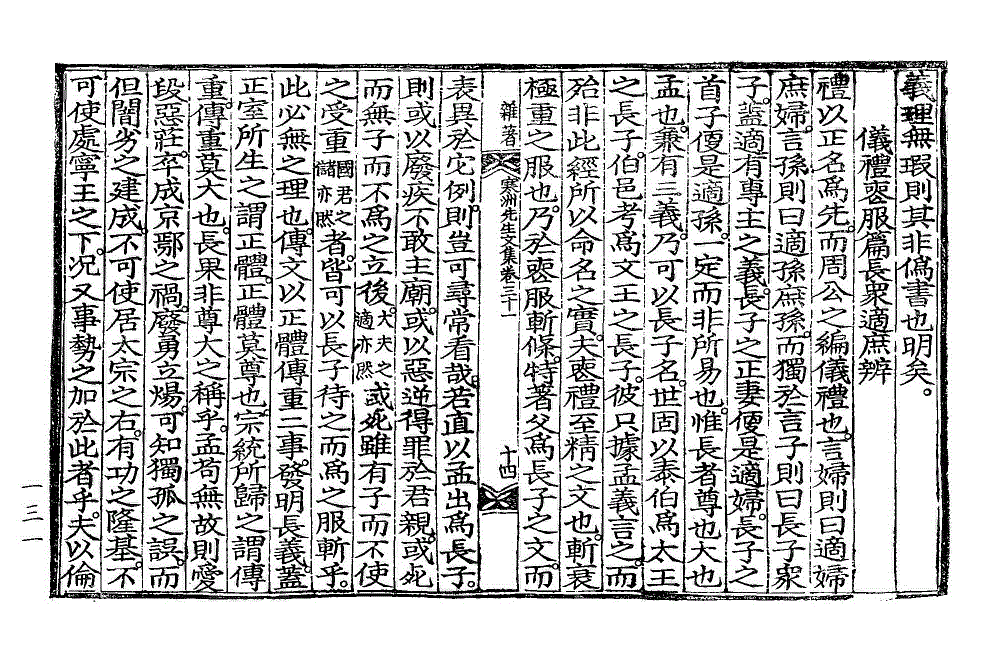 义理无瑕则其非伪书也明矣。
义理无瑕则其非伪书也明矣。仪礼丧服篇长众适庶辨
礼以正名为先。而周公之编仪礼也。言妇则曰适妇庶妇。言孙则曰适孙庶孙。而独于言子则曰长子众子。盖适有专主之义。长子之正妻便是适妇。长子之首子便是适孙。一定而非所易也。惟长者尊也大也孟也。兼有三义。乃可以长子名。世固以泰伯为太王之长子。伯邑考为文王之长子。彼只据孟义言之。而殆非此经所以命名之实。夫丧礼至精之文也。斩衰极重之服也。乃于丧服斩条。特著父为长子之文。而表异于它例。则岂可寻常看哉。若直以孟出为长子。则或以废疾不敢主庙。或以恶逆得罪于君亲。或死而无子而不为之立后。(大夫之适亦然)或死虽有子而不使之受重(国君之储亦然)者。皆可以长子待之而为之服斩乎。此必无之理也。传文以正体传重二事。发明长义。盖正室所生之谓正体。正体莫尊也。宗统所归之谓传重。传重莫大也。长果非尊大之称乎。孟苟无故则爱段恶庄。卒成京鄢之祸。废勇立炀。可知独孤之误。而但闇劣之建成。不可使居太宗之右。有功之隆基。不可使处宁王之下。况又事势之加于此者乎。夫以伦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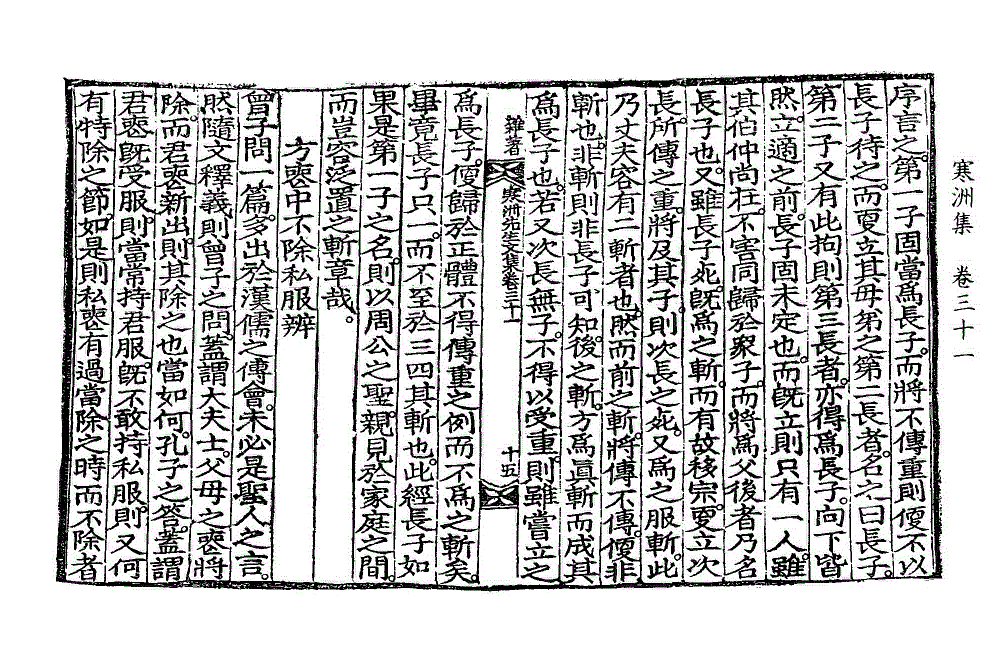 序言之。第一子固当为长子。而将不传重则便不以长子待之。而更立其母弟之第二长者。名之曰长子。第二子又有此拘则第三长者。亦得为长子。向下皆然。立适之前。长子固未定也。而既立则只有一人。虽其伯仲尚在。不害同归于众子。而将为父后者乃名长子也。又虽长子死。既为之斩。而有故移宗。更立次长。所传之重。将及其子。则次长之死。又为之服斩。此乃丈夫容有二斩者也。然而前之斩。将传不传。便非斩也。非斩则非长子可知。后之斩。方为真斩而成其为长子也。若又次长无子。不得以受重。则虽尝立之为长子。便归于正体不得传重之例而不为之斩矣。毕竟长子只一。而不至于三四其斩也。此经长子如果是第一子之名。则以周公之圣。亲见于家庭之间。而岂容泛置之斩章哉。
序言之。第一子固当为长子。而将不传重则便不以长子待之。而更立其母弟之第二长者。名之曰长子。第二子又有此拘则第三长者。亦得为长子。向下皆然。立适之前。长子固未定也。而既立则只有一人。虽其伯仲尚在。不害同归于众子。而将为父后者乃名长子也。又虽长子死。既为之斩。而有故移宗。更立次长。所传之重。将及其子。则次长之死。又为之服斩。此乃丈夫容有二斩者也。然而前之斩。将传不传。便非斩也。非斩则非长子可知。后之斩。方为真斩而成其为长子也。若又次长无子。不得以受重。则虽尝立之为长子。便归于正体不得传重之例而不为之斩矣。毕竟长子只一。而不至于三四其斩也。此经长子如果是第一子之名。则以周公之圣。亲见于家庭之间。而岂容泛置之斩章哉。方丧中不除私服辨
曾子问一篇。多出于汉儒之傅会。未必是圣人之言。然随文释义则曾子之问。盖谓太夫士。父母之丧将除。而君丧新出。则其除之也当如何。孔子之答。盖谓君丧既受服。则当常持君服。既不敢持私服。则又何有特除之节。如是则私丧有过当除之时而不除者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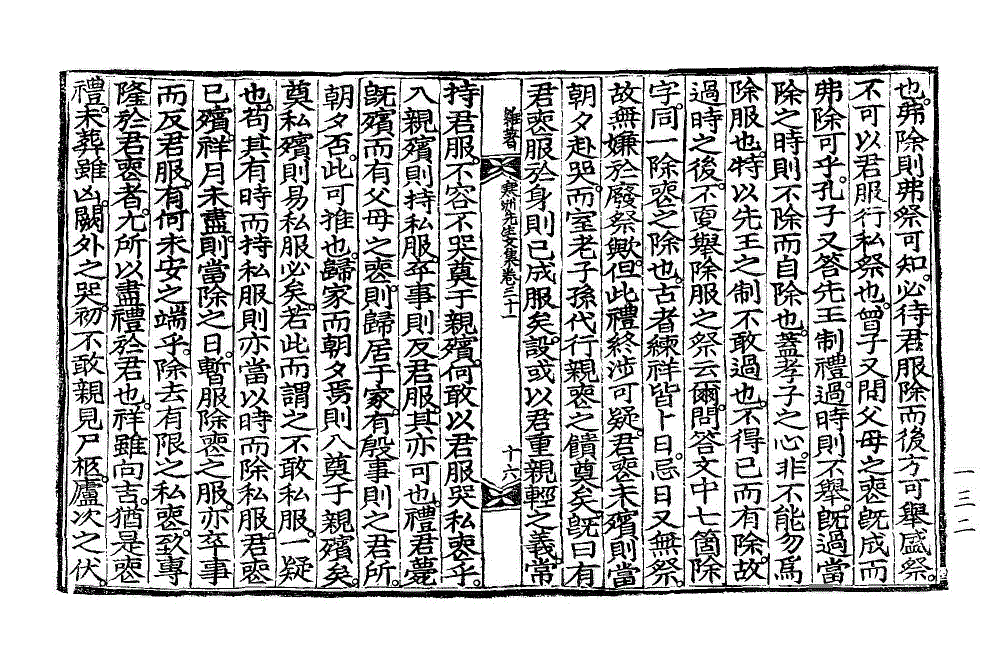 也。弗除则弗祭可知。必待君服除而后方可举盛祭。不可以君服行私祭也。曾子又问父母之丧既成而弗除可乎。孔子又答先王制礼。过时则不举。既过当除之时则不除而自除也。盖孝子之心。非不能勿为除服也。特以先王之制不敢过也。不得已而有除。故过时之后。不更举除服之祭云尔。问答文中七个除字。同一除丧之除也。古者练祥皆卜日。忌日又无祭。故无嫌于废祭欤。但此礼终涉可疑。君丧未殡则当朝夕赴哭。而室老子孙代行亲丧之馈奠矣。既曰有君丧服于身则已成服矣。设或以君重亲轻之义。常持君服。不容不哭奠于亲殡。何敢以君服哭私丧乎。入亲殡则持私服。卒事则反君服。其亦可也。礼君薨既殡而有父母之丧。则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此可推也。归家而朝夕焉则入奠于亲殡矣。奠私殡则易私服必矣。若此而谓之不敢私服。一疑也。苟其有时而持私服则亦当以时而除私服。君丧已殡。祥月未尽。则当除之日。暂服除丧之服。亦卒事而反君服。有何未安之端乎。除去有限之私丧。致专隆于君丧者。尤所以尽礼于君也。祥虽向吉。犹是丧礼。未葬虽凶。阙外之哭。初不敢亲见尸柩。庐次之伏。
也。弗除则弗祭可知。必待君服除而后方可举盛祭。不可以君服行私祭也。曾子又问父母之丧既成而弗除可乎。孔子又答先王制礼。过时则不举。既过当除之时则不除而自除也。盖孝子之心。非不能勿为除服也。特以先王之制不敢过也。不得已而有除。故过时之后。不更举除服之祭云尔。问答文中七个除字。同一除丧之除也。古者练祥皆卜日。忌日又无祭。故无嫌于废祭欤。但此礼终涉可疑。君丧未殡则当朝夕赴哭。而室老子孙代行亲丧之馈奠矣。既曰有君丧服于身则已成服矣。设或以君重亲轻之义。常持君服。不容不哭奠于亲殡。何敢以君服哭私丧乎。入亲殡则持私服。卒事则反君服。其亦可也。礼君薨既殡而有父母之丧。则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此可推也。归家而朝夕焉则入奠于亲殡矣。奠私殡则易私服必矣。若此而谓之不敢私服。一疑也。苟其有时而持私服则亦当以时而除私服。君丧已殡。祥月未尽。则当除之日。暂服除丧之服。亦卒事而反君服。有何未安之端乎。除去有限之私丧。致专隆于君丧者。尤所以尽礼于君也。祥虽向吉。犹是丧礼。未葬虽凶。阙外之哭。初不敢亲见尸柩。庐次之伏。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3H 页
 未必垢墨其面。不可以凶时行吉礼论。如父母偕丧者也。礼君未殡而有父母之丧。则归殡返于君所。有殷事则归。说者以朔望奠为殷事。未殡之日。尚有殷事之奠。则已殡之日。独不得设奠除之乎。服只是生者之事。初非为除而祭。则何必设盛祭然后可除也。苟其设奠。可以除服。则虽在未殡之前。当据殷事归之文。哭除于当除之日矣。若此而谓之又何除焉。二疑也。服不可有成而无除。不除于当除之时。则过时犹可除也。故父丧将除而有祖丧则祖卒哭后除服。母丧将除而有父丧则父卒哭后除服。况此君丧非如同宫之拘。则私丧祭除。自可依时。何有乎过时哉。此三疑也。三年都毕。方谓之服除。而练祥亦自是殷祭。非必时祭而后谓之殷祭也。礼丧三年不祭。以其不行时祭也。三年之丧既顈。其练祥皆行。则君丧未除。时祭或可不行。而练祥何可不行。练祥可行则服未除。尚可殷祭。此四疑也。礼莫重于葬。而历考传记。天子之葬有过七月之期者。诸侯之葬有过五月之期者。苟有大故。不加贬词。且三年而葬。士庶犹然。虽以祭礼言之。父丧中先葬母不虞祔待后事。则虞或在三月之后。三年而葬者。以葬之后月练。以练之次
未必垢墨其面。不可以凶时行吉礼论。如父母偕丧者也。礼君未殡而有父母之丧。则归殡返于君所。有殷事则归。说者以朔望奠为殷事。未殡之日。尚有殷事之奠。则已殡之日。独不得设奠除之乎。服只是生者之事。初非为除而祭。则何必设盛祭然后可除也。苟其设奠。可以除服。则虽在未殡之前。当据殷事归之文。哭除于当除之日矣。若此而谓之又何除焉。二疑也。服不可有成而无除。不除于当除之时。则过时犹可除也。故父丧将除而有祖丧则祖卒哭后除服。母丧将除而有父丧则父卒哭后除服。况此君丧非如同宫之拘。则私丧祭除。自可依时。何有乎过时哉。此三疑也。三年都毕。方谓之服除。而练祥亦自是殷祭。非必时祭而后谓之殷祭也。礼丧三年不祭。以其不行时祭也。三年之丧既顈。其练祥皆行。则君丧未除。时祭或可不行。而练祥何可不行。练祥可行则服未除。尚可殷祭。此四疑也。礼莫重于葬。而历考传记。天子之葬有过七月之期者。诸侯之葬有过五月之期者。苟有大故。不加贬词。且三年而葬。士庶犹然。虽以祭礼言之。父丧中先葬母不虞祔待后事。则虞或在三月之后。三年而葬者。以葬之后月练。以练之次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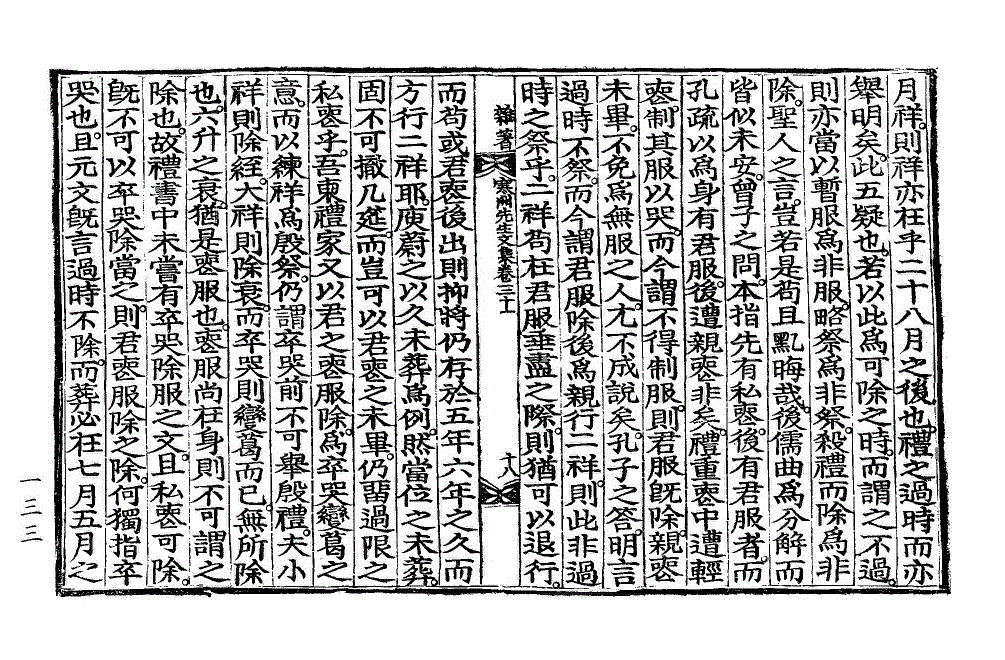 月祥。则祥亦在乎二十八月之后也。礼之过时而亦举明矣。此五疑也。若以此为可除之时。而谓之不过。则亦当以暂服为非服。略祭为非祭。杀礼而除为非除。圣人之言。岂若是苟且䵝晦哉。后儒曲为分解而皆似未安。曾子之问。本指先有私丧。后有君服者。而孔疏以为身有君服。后遭亲丧非矣。礼重丧中遭轻丧。制其服以哭。而今谓不得制服。则君服既除。亲丧未毕。不免为无服之人。尤不成说矣。孔子之答。明言过时不祭。而今谓君服除后为亲行二祥。则此非过时之祭乎。二祥苟在君服垂尽之际。则犹可以退行。而苟或君丧后出则抑将仍存于五年六年之久而方行二祥耶。庾蔚之以久未葬为例。然当位之未葬。固不可撤几筵。而岂可以君丧之未毕。仍留过限之私丧乎。吾东礼家又以君之丧服除。为卒哭变葛之意。而以练祥为殷祭。仍谓卒哭前不可举殷礼。夫小祥则除绖。大祥则除衰。而卒哭则变葛而已。无所除也。六升之衰。犹是丧服也。丧服尚在身则不可谓之除也。故礼书中未尝有卒哭除服之文。且私丧可除。既不可以卒哭除当之。则君丧服除之除。何独指卒哭也。且元文既言过时不除。而葬必在七月五月之
月祥。则祥亦在乎二十八月之后也。礼之过时而亦举明矣。此五疑也。若以此为可除之时。而谓之不过。则亦当以暂服为非服。略祭为非祭。杀礼而除为非除。圣人之言。岂若是苟且䵝晦哉。后儒曲为分解而皆似未安。曾子之问。本指先有私丧。后有君服者。而孔疏以为身有君服。后遭亲丧非矣。礼重丧中遭轻丧。制其服以哭。而今谓不得制服。则君服既除。亲丧未毕。不免为无服之人。尤不成说矣。孔子之答。明言过时不祭。而今谓君服除后为亲行二祥。则此非过时之祭乎。二祥苟在君服垂尽之际。则犹可以退行。而苟或君丧后出则抑将仍存于五年六年之久而方行二祥耶。庾蔚之以久未葬为例。然当位之未葬。固不可撤几筵。而岂可以君丧之未毕。仍留过限之私丧乎。吾东礼家又以君之丧服除。为卒哭变葛之意。而以练祥为殷祭。仍谓卒哭前不可举殷礼。夫小祥则除绖。大祥则除衰。而卒哭则变葛而已。无所除也。六升之衰。犹是丧服也。丧服尚在身则不可谓之除也。故礼书中未尝有卒哭除服之文。且私丧可除。既不可以卒哭除当之。则君丧服除之除。何独指卒哭也。且元文既言过时不除。而葬必在七月五月之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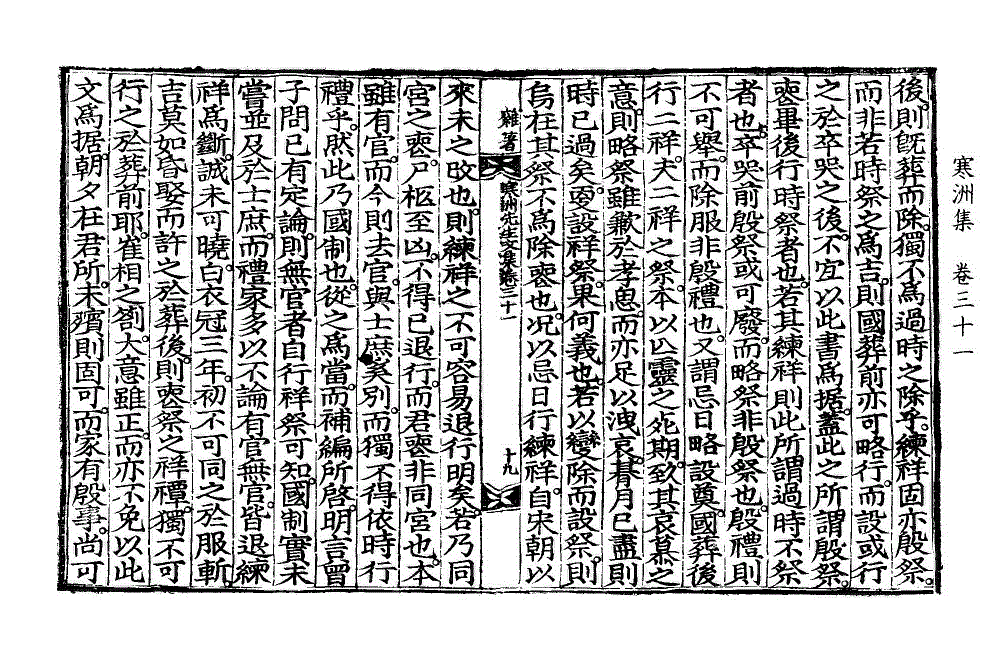 后。则既葬而除。独不为过时之除乎。练祥固亦殷祭。而非若时祭之为吉。则国葬前亦可略行。而设或行之于卒哭之后。不宜以此书为据。盖此之所谓殷祭。丧毕后行时祭者也。若其练祥则此所谓过时不祭者也。卒哭前殷祭或可废。而略祭非殷祭也。殷礼则不可举。而除服非殷礼也。又谓忌日略设奠。国葬后行二祥。夫二祥之祭。本以亡灵之死期。致其哀慕之意。则略祭虽歉于孝思。而亦足以泄哀。期月已尽则时已过矣。更设祥祭。果何义也。若以变除而设祭。则乌在其祭不为除丧也。况以忌日行练祥。自宋朝以来未之改也。则练祥之不可容易退行明矣。若乃同宫之丧。尸柩至凶。不得已退行。而君丧非同宫也。本虽有官。而今则去官。与士庶奚别。而独不得依时行礼乎。然此乃国制也。从之为当。而补编所启。明言曾子问已有定论。则无官者自行祥祭可知。国制实未尝并及于士庶。而礼家多以不论有官无官。皆退练祥为断。诚未可晓。白衣冠三年。初不可同之于服斩。吉莫如昏娶而许之于葬后。则丧祭之祥禫。独不可行之于葬前耶。崔相之劄。大意虽正。而亦不免以此文为据。朝夕在君所。未殡则固可。而家有殷事。尚可
后。则既葬而除。独不为过时之除乎。练祥固亦殷祭。而非若时祭之为吉。则国葬前亦可略行。而设或行之于卒哭之后。不宜以此书为据。盖此之所谓殷祭。丧毕后行时祭者也。若其练祥则此所谓过时不祭者也。卒哭前殷祭或可废。而略祭非殷祭也。殷礼则不可举。而除服非殷礼也。又谓忌日略设奠。国葬后行二祥。夫二祥之祭。本以亡灵之死期。致其哀慕之意。则略祭虽歉于孝思。而亦足以泄哀。期月已尽则时已过矣。更设祥祭。果何义也。若以变除而设祭。则乌在其祭不为除丧也。况以忌日行练祥。自宋朝以来未之改也。则练祥之不可容易退行明矣。若乃同宫之丧。尸柩至凶。不得已退行。而君丧非同宫也。本虽有官。而今则去官。与士庶奚别。而独不得依时行礼乎。然此乃国制也。从之为当。而补编所启。明言曾子问已有定论。则无官者自行祥祭可知。国制实未尝并及于士庶。而礼家多以不论有官无官。皆退练祥为断。诚未可晓。白衣冠三年。初不可同之于服斩。吉莫如昏娶而许之于葬后。则丧祭之祥禫。独不可行之于葬前耶。崔相之劄。大意虽正。而亦不免以此文为据。朝夕在君所。未殡则固可。而家有殷事。尚可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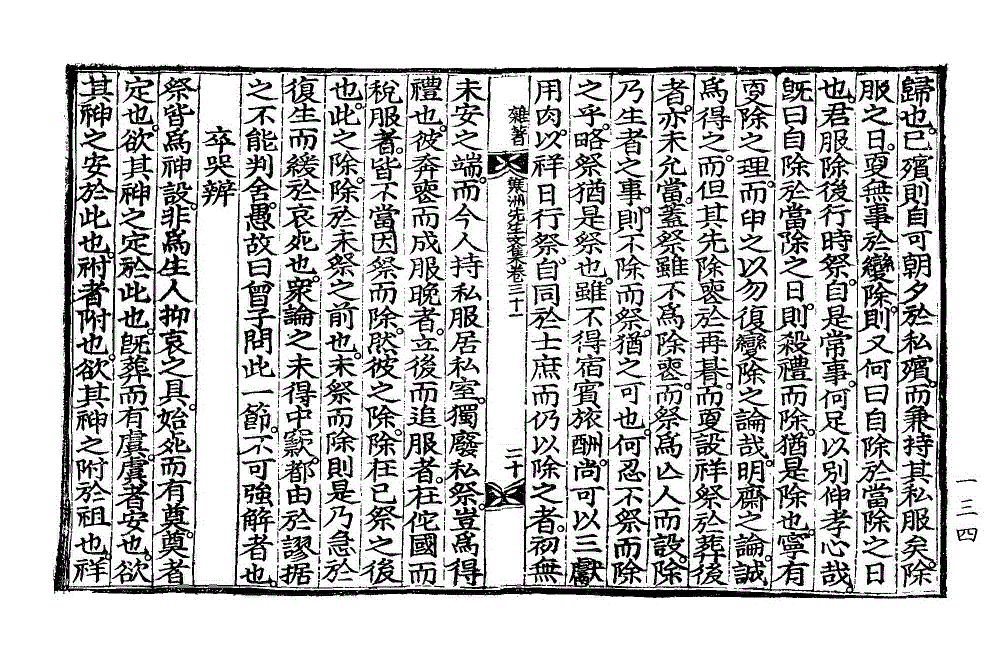 归也。已殡则自可朝夕于私殡。而兼持其私服矣。除服之日。更无事于变除。则又何曰自除于当除之日也。君服除后行时祭。自是常事。何足以别伸孝心哉。既曰自除于当除之日。则杀礼而除。犹是除也。宁有更除之理。而申之以勿复变除之论哉。明斋之论。诚为得之。而但其先除丧于再期。而更设祥祭于葬后者。亦未允当。盖祭虽不为除丧。而祭为亡人而设。除乃生者之事。则不除而祭。犹之可也。何忍不祭而除之乎。略祭犹是祭也。虽不得宿宾旅酬。尚可以三献用肉。以祥日行祭。自同于士庶而仍以除之者。初无未安之端。而今人持私服居私室。独废私祭。岂为得礼也。彼奔丧而成服晚者。立后而追服者。在佗国而税服者。皆不当因祭而除。然彼之除。除在已祭之后也。此之除。除于未祭之前也。未祭而除则是乃急于复生而缓于哀死也。众论之未得中窾。都由于谬据之不能判舍。愚故曰曾子问此一节。不可强解者也。
归也。已殡则自可朝夕于私殡。而兼持其私服矣。除服之日。更无事于变除。则又何曰自除于当除之日也。君服除后行时祭。自是常事。何足以别伸孝心哉。既曰自除于当除之日。则杀礼而除。犹是除也。宁有更除之理。而申之以勿复变除之论哉。明斋之论。诚为得之。而但其先除丧于再期。而更设祥祭于葬后者。亦未允当。盖祭虽不为除丧。而祭为亡人而设。除乃生者之事。则不除而祭。犹之可也。何忍不祭而除之乎。略祭犹是祭也。虽不得宿宾旅酬。尚可以三献用肉。以祥日行祭。自同于士庶而仍以除之者。初无未安之端。而今人持私服居私室。独废私祭。岂为得礼也。彼奔丧而成服晚者。立后而追服者。在佗国而税服者。皆不当因祭而除。然彼之除。除在已祭之后也。此之除。除于未祭之前也。未祭而除则是乃急于复生而缓于哀死也。众论之未得中窾。都由于谬据之不能判舍。愚故曰曾子问此一节。不可强解者也。卒哭辨
祭皆为神设。非为生人抑哀之具。始死而有奠。奠者定也。欲其神之定于此也。既葬而有虞。虞者安也。欲其神之安于此也。祔者附也。欲其神之附于祖也。祥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5H 页
 者吉也。小祥以吉主(栗主为吉。桑主为丧。)祭于庙。大祥则永迁于庙。殡凶庙吉。神道自凶而趋吉也。禫者澹也。欲其神之于庙。澹澹然平安也。如葬毕之有虞祫者。合而欲其神之于祖。恰恰然孚合也。如虞毕之有祔。皆所以保固亡灵。不至于飘散也。惟虞祔之间。有所谓卒哭之祭。卒去非时之哭。孝子事也。何关于神道而为之祭乎。且初虞之祝曰祫事。再虞曰虞事。祔曰祔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禫祫亦各举其事。而独三虞卒哭两祭。并称成事。何其一事而两祭也。愚窃惑焉。按既夕礼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此言三虞既行。始卒非时之哭。而仍祔于其翌也。非谓虞祔之间。更有卒哭之祭也。士虞记曰三虞卒哭。佗用刚日。盖诸侯七虞而卒哭。大夫五虞而卒哭。三虞卒哭。惟士为然。故连说之。所以明未三虞则不可卒哭。非卒哭则不用刚日。佗者别也。别用刚日。成事故也。非谓三虞与卒哭及佗祭。皆用刚日。皆云成事也。又曰三月而葬遂卒哭。将朝而祔。则荐卒辞云云。此承上三哭而言。士以葬月便卒哭。非谓葬毕。只行卒哭之祭也。将以明日祔。故荐礼之终。告以隮附之意。非谓将祔则有荐。不祔则无荐也。亦非谓卒哭祝辞只有此
者吉也。小祥以吉主(栗主为吉。桑主为丧。)祭于庙。大祥则永迁于庙。殡凶庙吉。神道自凶而趋吉也。禫者澹也。欲其神之于庙。澹澹然平安也。如葬毕之有虞祫者。合而欲其神之于祖。恰恰然孚合也。如虞毕之有祔。皆所以保固亡灵。不至于飘散也。惟虞祔之间。有所谓卒哭之祭。卒去非时之哭。孝子事也。何关于神道而为之祭乎。且初虞之祝曰祫事。再虞曰虞事。祔曰祔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禫祫亦各举其事。而独三虞卒哭两祭。并称成事。何其一事而两祭也。愚窃惑焉。按既夕礼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此言三虞既行。始卒非时之哭。而仍祔于其翌也。非谓虞祔之间。更有卒哭之祭也。士虞记曰三虞卒哭。佗用刚日。盖诸侯七虞而卒哭。大夫五虞而卒哭。三虞卒哭。惟士为然。故连说之。所以明未三虞则不可卒哭。非卒哭则不用刚日。佗者别也。别用刚日。成事故也。非谓三虞与卒哭及佗祭。皆用刚日。皆云成事也。又曰三月而葬遂卒哭。将朝而祔。则荐卒辞云云。此承上三哭而言。士以葬月便卒哭。非谓葬毕。只行卒哭之祭也。将以明日祔。故荐礼之终。告以隮附之意。非谓将祔则有荐。不祔则无荐也。亦非谓卒哭祝辞只有此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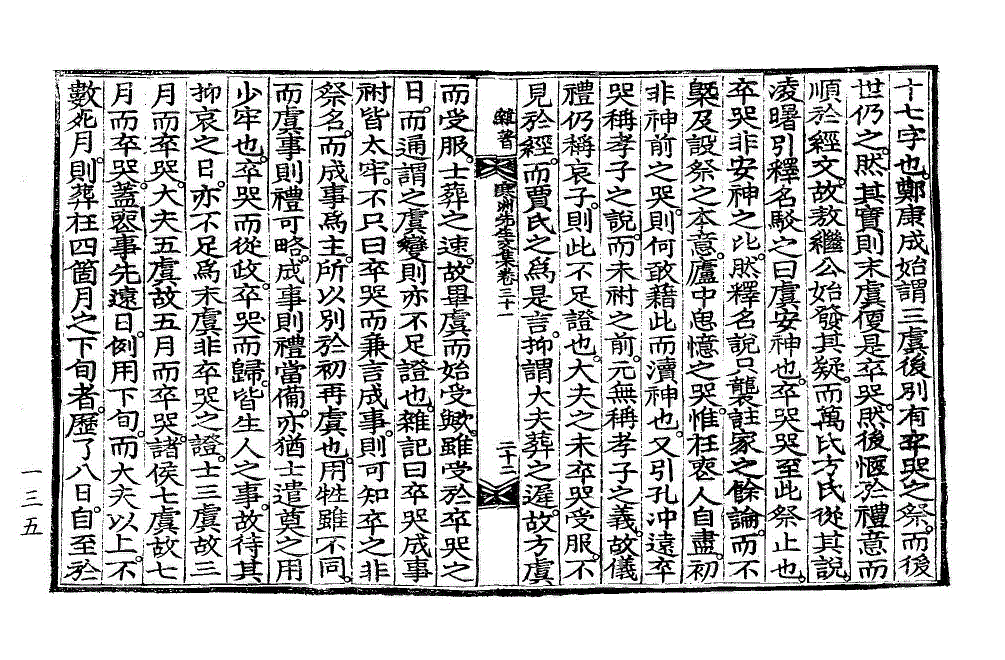 十七字也。郑康成始谓三虞后别有卒哭之祭。而后世仍之。然其实则末虞便是卒哭。然后惬于礼意而顺于经文。故敖继公始发其疑。而万氏方氏从其说。凌曙引释名驳之曰虞安神也。卒哭哭至此祭止也。卒哭非安神之比。然释名说只袭注家之馀论。而不槩及设祭之本意。庐中思忆之哭。惟在丧人自尽。初非神前之哭。则何敢藉此而渎神也。又引孔冲远卒哭称孝子之说。而未祔之前。元无称孝子之义。故仪礼仍称哀子。则此不足證也。大夫之未卒哭受服。不见于经。而贾氏之为是言。抑谓大夫葬之迟。故方虞而受服。士葬之速。故毕虞而始受欤。虽受于卒哭之日。而通谓之虞变则亦不足證也。杂记曰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不只曰卒哭而兼言成事。则可知卒之非祭名。而成事为主。所以别于初再虞也。用牲虽不同。而虞事则礼可略。成事则礼当备。亦犹士遣奠之用少牢也。卒哭而从政。卒哭而归。皆生人之事。故待其抑哀之日。亦不足为末虞非卒哭之證。士三虞故三月而卒哭。大夫五虞故五月而卒哭。诸侯七虞故七月而卒哭。盖丧事先远日。例用下旬。而大夫以上。不数死月。则葬在四个月之下旬者。历了八日。自至于
十七字也。郑康成始谓三虞后别有卒哭之祭。而后世仍之。然其实则末虞便是卒哭。然后惬于礼意而顺于经文。故敖继公始发其疑。而万氏方氏从其说。凌曙引释名驳之曰虞安神也。卒哭哭至此祭止也。卒哭非安神之比。然释名说只袭注家之馀论。而不槩及设祭之本意。庐中思忆之哭。惟在丧人自尽。初非神前之哭。则何敢藉此而渎神也。又引孔冲远卒哭称孝子之说。而未祔之前。元无称孝子之义。故仪礼仍称哀子。则此不足證也。大夫之未卒哭受服。不见于经。而贾氏之为是言。抑谓大夫葬之迟。故方虞而受服。士葬之速。故毕虞而始受欤。虽受于卒哭之日。而通谓之虞变则亦不足證也。杂记曰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不只曰卒哭而兼言成事。则可知卒之非祭名。而成事为主。所以别于初再虞也。用牲虽不同。而虞事则礼可略。成事则礼当备。亦犹士遣奠之用少牢也。卒哭而从政。卒哭而归。皆生人之事。故待其抑哀之日。亦不足为末虞非卒哭之證。士三虞故三月而卒哭。大夫五虞故五月而卒哭。诸侯七虞故七月而卒哭。盖丧事先远日。例用下旬。而大夫以上。不数死月。则葬在四个月之下旬者。历了八日。自至于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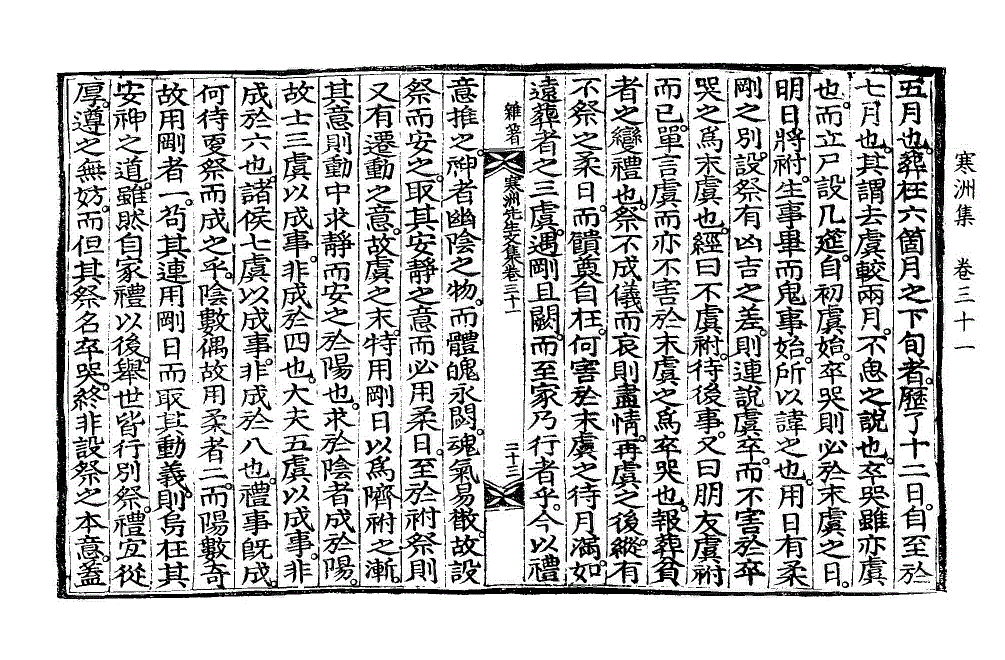 五月也。葬在六个月之下旬者。历了十二日。自至于七月也。其谓去虞较两月。不思之说也。卒哭虽亦虞也。而立尸设几筵。自初虞始。卒哭则必于末虞之日。明日将祔。生事毕而鬼事始。所以讳之也。用日有柔刚之别。设祭有凶吉之差。则连说虞卒。而不害于卒哭之为末虞也。经曰不虞祔。待后事。又曰明友虞祔而已。单言虞而亦不害于末虞之为卒哭也。报葬贫者之变礼也。祭不成仪而哀则尽情。再虞之后。纵有不祭之柔日。而馈奠自在。何害于末虞之待月满。如远葬者之三虞。遇刚且阙。而至家乃行者乎。今以礼意推之。神者幽阴之物。而体魄永閟。魂气易散。故设祭而安之。取其安静之意而必用柔日。至于祔祭则又有迁动之意。故虞之末。特用刚日以为隮祔之渐。其意则动中求静而安之于阳也。求于阴者成于阳。故士三虞以成事。非成于四也。大夫五虞以成事。非成于六也。诸侯七虞以成事。非成于八也。礼事既成。何待更祭而成之乎。阴数偶故用柔者二。而阳数奇故用刚者一。苟其连用刚日而取其动义。则乌在其安神之道。虽然自家礼以后。举世皆行别祭。礼宜从厚。遵之无妨。而但其祭名卒哭。终非设祭之本意。盖
五月也。葬在六个月之下旬者。历了十二日。自至于七月也。其谓去虞较两月。不思之说也。卒哭虽亦虞也。而立尸设几筵。自初虞始。卒哭则必于末虞之日。明日将祔。生事毕而鬼事始。所以讳之也。用日有柔刚之别。设祭有凶吉之差。则连说虞卒。而不害于卒哭之为末虞也。经曰不虞祔。待后事。又曰明友虞祔而已。单言虞而亦不害于末虞之为卒哭也。报葬贫者之变礼也。祭不成仪而哀则尽情。再虞之后。纵有不祭之柔日。而馈奠自在。何害于末虞之待月满。如远葬者之三虞。遇刚且阙。而至家乃行者乎。今以礼意推之。神者幽阴之物。而体魄永閟。魂气易散。故设祭而安之。取其安静之意而必用柔日。至于祔祭则又有迁动之意。故虞之末。特用刚日以为隮祔之渐。其意则动中求静而安之于阳也。求于阴者成于阳。故士三虞以成事。非成于四也。大夫五虞以成事。非成于六也。诸侯七虞以成事。非成于八也。礼事既成。何待更祭而成之乎。阴数偶故用柔者二。而阳数奇故用刚者一。苟其连用刚日而取其动义。则乌在其安神之道。虽然自家礼以后。举世皆行别祭。礼宜从厚。遵之无妨。而但其祭名卒哭。终非设祭之本意。盖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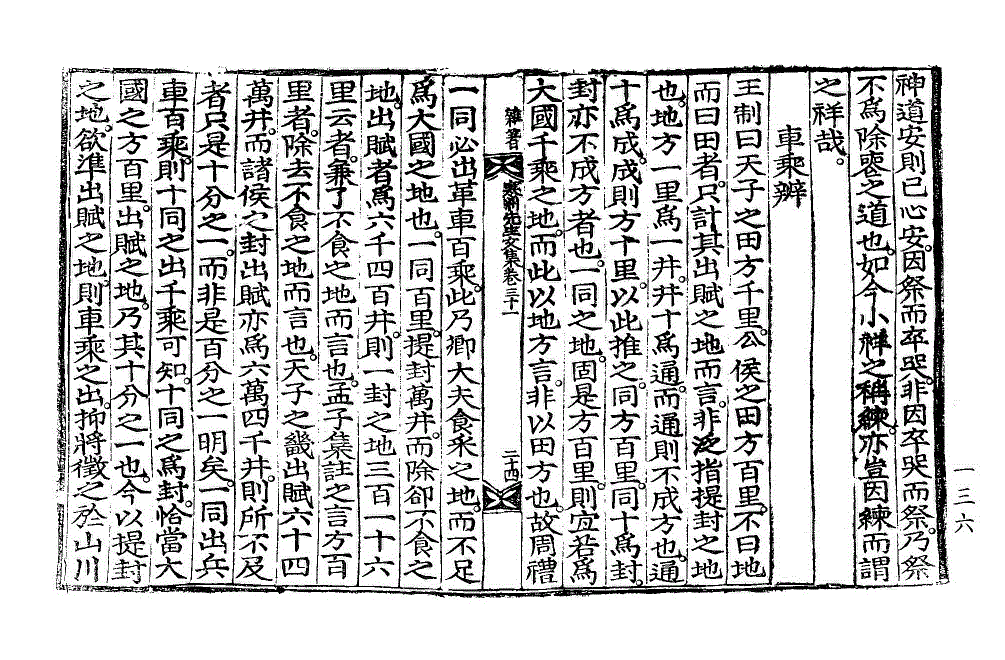 神道安则已心安。因祭而卒哭。非因卒哭而祭。乃祭不为除丧之道也。如今小祥之称练。亦岂因练而谓之祥哉。
神道安则已心安。因祭而卒哭。非因卒哭而祭。乃祭不为除丧之道也。如今小祥之称练。亦岂因练而谓之祥哉。车乘辨
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不曰地而曰田者。只计其出赋之地而言。非泛指提封之地也。地方一里为一井。井十为通。而通则不成方也。通十为成。成则方十里。以此推之。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亦不成方者也。一同之地。固是方百里。则宜若为大国千乘之地。而此以地方言。非以田方也。故周礼一同必出革车百乘。此乃卿大夫食采之地。而不足为大国之地也。一同百里。提封万井。而除却不食之地。出赋者为六千四百井。则一封之地三百一十六里云者。兼了不食之地而言也。孟子集注之言方百里者。除去不食之地而言也。天子之畿出赋六十四万井。而诸侯之封出赋亦为六万四千井。则所不及者只是十分之一。而非是百分之一明矣。一同出兵车百乘。则十同之出千乘可知。十同之为封。恰当大国之方百里。出赋之地。乃其十分之一也。今以提封之地。欲准出赋之地。则车乘之出。抑将徵之于山川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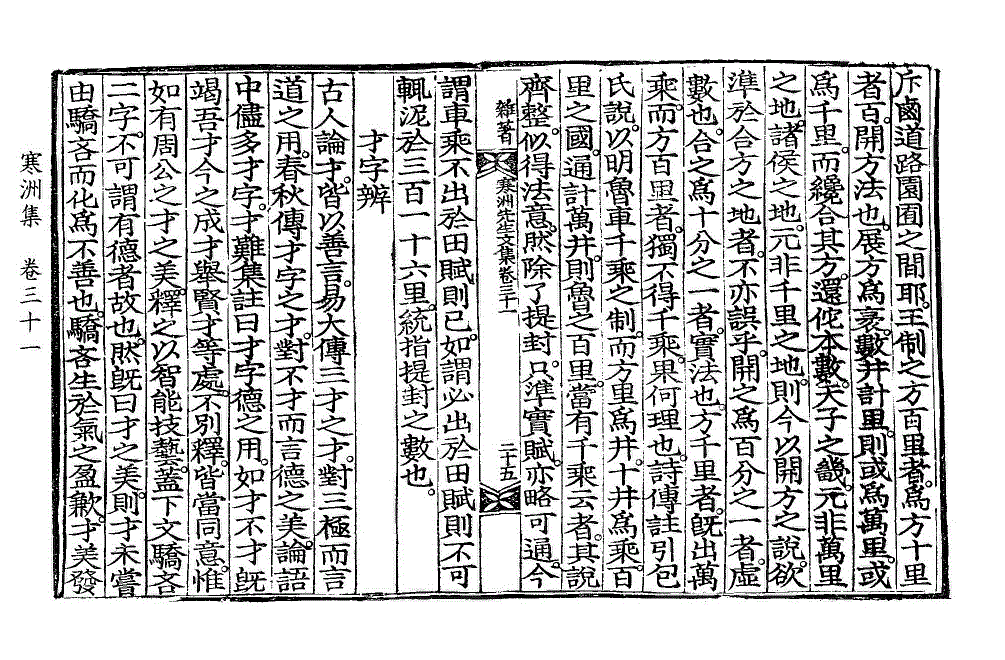 斥卤道路园囿之间耶。王制之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开方法也。展方为袤。数井计里。则或为万里。或为千里。而才合其方。还佗本数。天子之畿。元非万里之地。诸侯之地。元非千里之地。则今以开方之说。欲准于合方之地者。不亦误乎。开之为百分之一者。虚数也。合之为十分之一者。实法也。方千里者。既出万乘。而方百里者。独不得千乘。果何理也。诗传注引包氏说。以明鲁车千乘之制。而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通计万井。则鲁之百里。当有千乘云者。其说齐整。似得法意。然除了提封。只准实赋。亦略可通。今谓车乘不出于田赋则已。如谓必出于田赋则不可辄泥于三百一十六里。统指提封之数也。
斥卤道路园囿之间耶。王制之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开方法也。展方为袤。数井计里。则或为万里。或为千里。而才合其方。还佗本数。天子之畿。元非万里之地。诸侯之地。元非千里之地。则今以开方之说。欲准于合方之地者。不亦误乎。开之为百分之一者。虚数也。合之为十分之一者。实法也。方千里者。既出万乘。而方百里者。独不得千乘。果何理也。诗传注引包氏说。以明鲁车千乘之制。而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通计万井。则鲁之百里。当有千乘云者。其说齐整。似得法意。然除了提封。只准实赋。亦略可通。今谓车乘不出于田赋则已。如谓必出于田赋则不可辄泥于三百一十六里。统指提封之数也。才字辨
古人论才。皆以善言。易大传三才之才。对三极而言道之用。春秋传才字之才。对不才而言德之美。论语中尽多才字。才难集注曰才字德之用。如才不才既竭吾才今之成才举贤才等处。不别释。皆当同意。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释之以智能技艺。盖下文骄吝二字。不可谓有德者故也。然既曰才之美。则才未尝由骄吝而化为不善也。骄吝生于气之盈歉。才美发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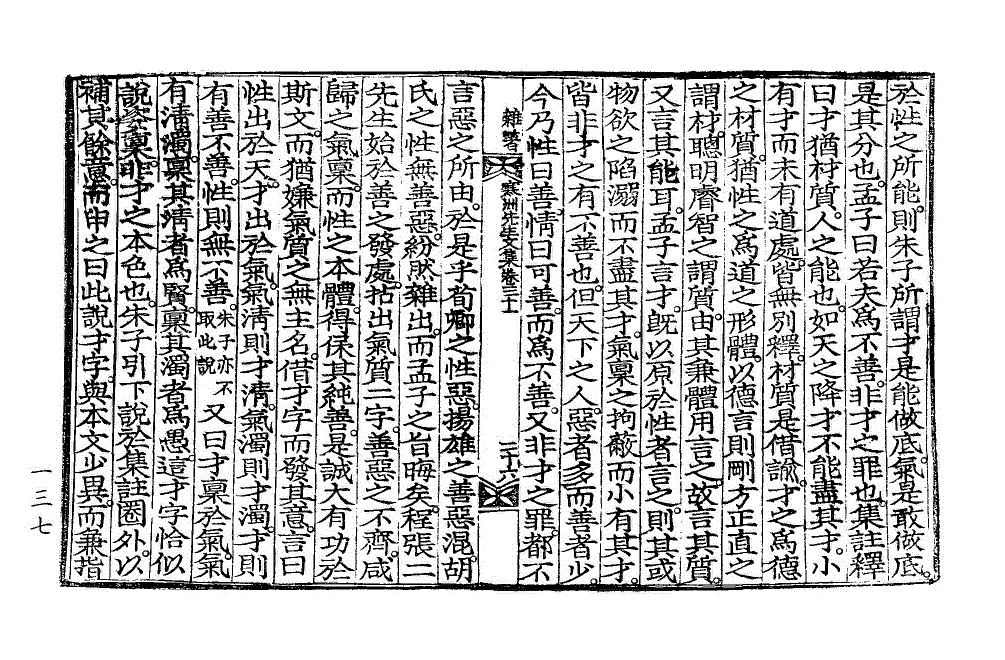 于性之所能。则朱子所谓才是能做底。气是敢做底。是其分也。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集注释曰才犹材质。人之能也。如天之降才不能尽其才。小有才而未有道处。皆无别释。材质是借谕。才之为德之材质。犹性之为道之形体。以德言则刚方正直之谓材。聪明睿智之谓质。由其兼体用言之。故言其质。又言其能耳。孟子言才。既以原于性者言之。则其或物欲之陷溺而不尽其才。气禀之拘蔽而小有其才。皆非才之有不善也。但天下之人。恶者多而善。者少。今乃性曰善。情曰可善。而为不善。又非才之罪。都不言恶之所由。于是乎荀卿之性恶。杨雄之善恶混。胡氏之性无善恶。纷然杂出。而孟子之旨晦矣。程张二先生始于善之发处。拈出气质二字。善恶之不齐。咸归之气禀。而性之本体。得保其纯善。是诚大有功于斯文。而犹嫌气质之无主名。借才字而发其意。言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朱子亦不取此说)又曰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才字恰似说姿禀。非才之本色也。朱子引下说于集注圈外。以补其馀意。而申之曰此说才字。与本文少异。而兼指
于性之所能。则朱子所谓才是能做底。气是敢做底。是其分也。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集注释曰才犹材质。人之能也。如天之降才不能尽其才。小有才而未有道处。皆无别释。材质是借谕。才之为德之材质。犹性之为道之形体。以德言则刚方正直之谓材。聪明睿智之谓质。由其兼体用言之。故言其质。又言其能耳。孟子言才。既以原于性者言之。则其或物欲之陷溺而不尽其才。气禀之拘蔽而小有其才。皆非才之有不善也。但天下之人。恶者多而善。者少。今乃性曰善。情曰可善。而为不善。又非才之罪。都不言恶之所由。于是乎荀卿之性恶。杨雄之善恶混。胡氏之性无善恶。纷然杂出。而孟子之旨晦矣。程张二先生始于善之发处。拈出气质二字。善恶之不齐。咸归之气禀。而性之本体。得保其纯善。是诚大有功于斯文。而犹嫌气质之无主名。借才字而发其意。言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朱子亦不取此说)又曰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才字恰似说姿禀。非才之本色也。朱子引下说于集注圈外。以补其馀意。而申之曰此说才字。与本文少异。而兼指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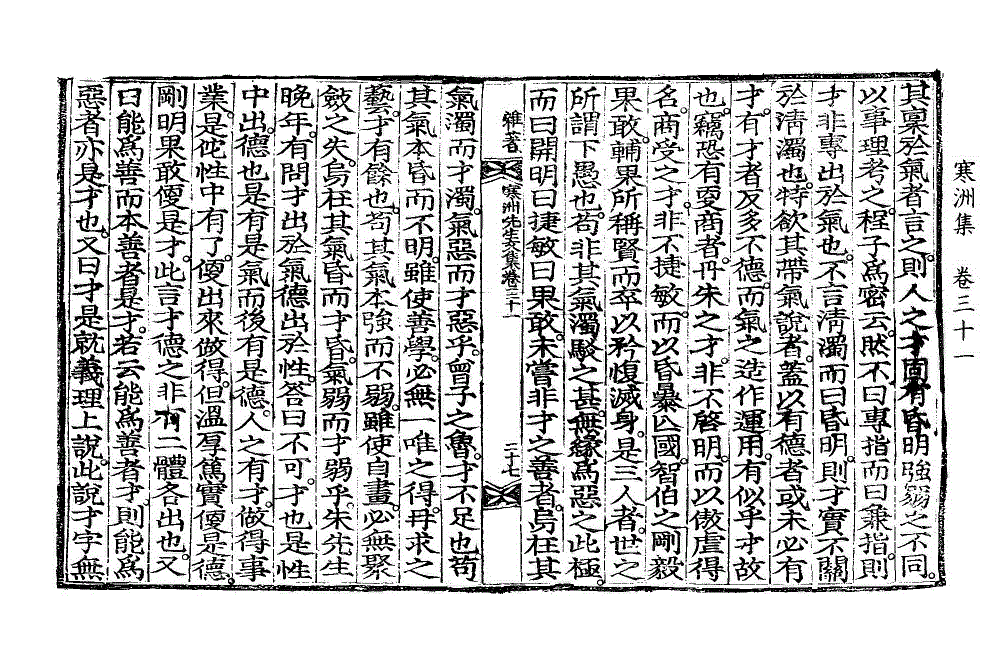 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云。然不曰专指而曰兼指。则才非专出于气也。不言清浊而曰昏明。则才实不关于清浊也。特欲其带气说者。盖以有德者或未必有才。有才者反多不德。而气之造作运用。有似乎才故也。窃恐有更商者。丹朱之才。非不启明。而以傲虐得名。商受之才。非不捷敏。而以昏㬥亡国。智伯之刚毅果敢。辅果所称贤而卒以矜愎灭身。是三人者。世之所谓下愚也。苟非其气浊驳之甚。无缘为恶之此极。而曰开明曰捷敏曰果敢。未尝非才之善者。乌在其气浊而才浊。气恶而才恶乎。曾子之鲁。才不足也。苟其气本昏而不明。虽使善学。必无一唯之得。冉求之艺。才有馀也。苟其气本强而不弱。虽使自画。必无聚敛之失。乌在其气昏而才昏。气弱而才弱乎。朱先生晚年。有问才出于气德出于性。答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气而后有是德。人之有才。做得事业。是佗性中有了。便出来做得。但温厚笃实便是德。刚明果敢便是才。此言才德之非有二体各出也。又曰能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为善者才。则能为恶者亦是才也。又曰才是就义理上说。此说才字无
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云。然不曰专指而曰兼指。则才非专出于气也。不言清浊而曰昏明。则才实不关于清浊也。特欲其带气说者。盖以有德者或未必有才。有才者反多不德。而气之造作运用。有似乎才故也。窃恐有更商者。丹朱之才。非不启明。而以傲虐得名。商受之才。非不捷敏。而以昏㬥亡国。智伯之刚毅果敢。辅果所称贤而卒以矜愎灭身。是三人者。世之所谓下愚也。苟非其气浊驳之甚。无缘为恶之此极。而曰开明曰捷敏曰果敢。未尝非才之善者。乌在其气浊而才浊。气恶而才恶乎。曾子之鲁。才不足也。苟其气本昏而不明。虽使善学。必无一唯之得。冉求之艺。才有馀也。苟其气本强而不弱。虽使自画。必无聚敛之失。乌在其气昏而才昏。气弱而才弱乎。朱先生晚年。有问才出于气德出于性。答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气而后有是德。人之有才。做得事业。是佗性中有了。便出来做得。但温厚笃实便是德。刚明果敢便是才。此言才德之非有二体各出也。又曰能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为善者才。则能为恶者亦是才也。又曰才是就义理上说。此说才字无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8L 页
 异于语孟之旨。皆以才之本色言之。则抑有初晚偏专之异耶。盖尝推之。禀五行之气。备有五常之性。仁之德温良而其才则易直。礼之德恭敬而其才则高明。信之德诚实而其才则博厚。义之德严毅而其才则果断。智之德贞固而其才则疏通。禀重浊之气者。德有馀而才不足。禀轻清之气者。才有馀而德不足。有馀不足。固由于气禀。而其才其德。实根于理性。德者理之实然底。才者理之能然底。气敢掩其德于昏浊。而不能息本体之明。气敢用其才于为恶。而不能变本质之美。则乌可以一时之偏言。硬定为气禀之变名也。程子之言。往往如此。性无不善而又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理自纯善而又谓善恶皆天理。此特发明气质之过。而不能无侵过界分者也。但曰性无不善而气拘之则善不遂。情可为善而气掩之则流于恶。为不善者非才之罪。而气之恶者。用其才于不善云则足矣。
异于语孟之旨。皆以才之本色言之。则抑有初晚偏专之异耶。盖尝推之。禀五行之气。备有五常之性。仁之德温良而其才则易直。礼之德恭敬而其才则高明。信之德诚实而其才则博厚。义之德严毅而其才则果断。智之德贞固而其才则疏通。禀重浊之气者。德有馀而才不足。禀轻清之气者。才有馀而德不足。有馀不足。固由于气禀。而其才其德。实根于理性。德者理之实然底。才者理之能然底。气敢掩其德于昏浊。而不能息本体之明。气敢用其才于为恶。而不能变本质之美。则乌可以一时之偏言。硬定为气禀之变名也。程子之言。往往如此。性无不善而又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理自纯善而又谓善恶皆天理。此特发明气质之过。而不能无侵过界分者也。但曰性无不善而气拘之则善不遂。情可为善而气掩之则流于恶。为不善者非才之罪。而气之恶者。用其才于不善云则足矣。志动气动辨(丙辰)
孟子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程子见其志气之有辨也。解之曰志动气者什九。气动志者什一。此则志气交动之机也。宋尤庵以太极为阴阳之主。證志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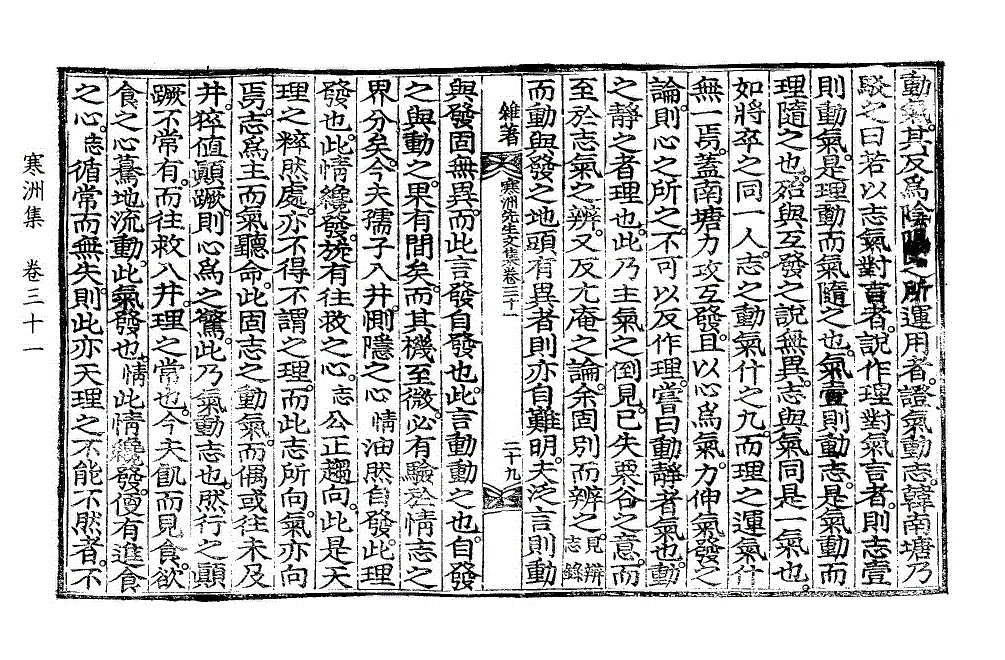 动气。其反为阴阳之所运用者。證气动志。韩南塘乃驳之曰若以志气对言者。说作理对气言者。则志壹则动气。是理动而气随之也。气壹则动志。是气动而理随之也。殆与互发之说无异。志与气同是一气也。如将卒之同一人。志之动气什之九。而理之运气什无一焉。盖南塘力攻互发。且以心为气。力伸气发之论。则心之所之。不可以反作理。尝曰动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此乃主气之倒见。已失栗谷之意。而至于志气之辨。又反尤庵之论。余固别而辨之。(见辨志录)而动与发之地头有异者则亦自难明。夫泛言则动与发固无异。而此言发自发也。此言动动之也。自发之与动之。果有间矣。而其机至微。必有验于情志之界分矣。今夫孺子入井。恻隐之心(情)油然自发。此理发也。此情才发。旋有往救之心。(志)公正趋向。此是天理之粹然处。亦不得不谓之理。而此志所向。气亦向焉。志为主而气听命。此固志之动气。而偶或往未及井。猝值颠蹶。则心为之惊。此乃气动志也。然行之颠蹶不常有。而往救入井。理之常也。今夫饥而见食。欲食之心蓦地流动。此气发也。(情)此情才发。便有进食之心。(志)循常而无失。则此亦天理之不能不然者。不
动气。其反为阴阳之所运用者。證气动志。韩南塘乃驳之曰若以志气对言者。说作理对气言者。则志壹则动气。是理动而气随之也。气壹则动志。是气动而理随之也。殆与互发之说无异。志与气同是一气也。如将卒之同一人。志之动气什之九。而理之运气什无一焉。盖南塘力攻互发。且以心为气。力伸气发之论。则心之所之。不可以反作理。尝曰动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此乃主气之倒见。已失栗谷之意。而至于志气之辨。又反尤庵之论。余固别而辨之。(见辨志录)而动与发之地头有异者则亦自难明。夫泛言则动与发固无异。而此言发自发也。此言动动之也。自发之与动之。果有间矣。而其机至微。必有验于情志之界分矣。今夫孺子入井。恻隐之心(情)油然自发。此理发也。此情才发。旋有往救之心。(志)公正趋向。此是天理之粹然处。亦不得不谓之理。而此志所向。气亦向焉。志为主而气听命。此固志之动气。而偶或往未及井。猝值颠蹶。则心为之惊。此乃气动志也。然行之颠蹶不常有。而往救入井。理之常也。今夫饥而见食。欲食之心蓦地流动。此气发也。(情)此情才发。便有进食之心。(志)循常而无失。则此亦天理之不能不然者。不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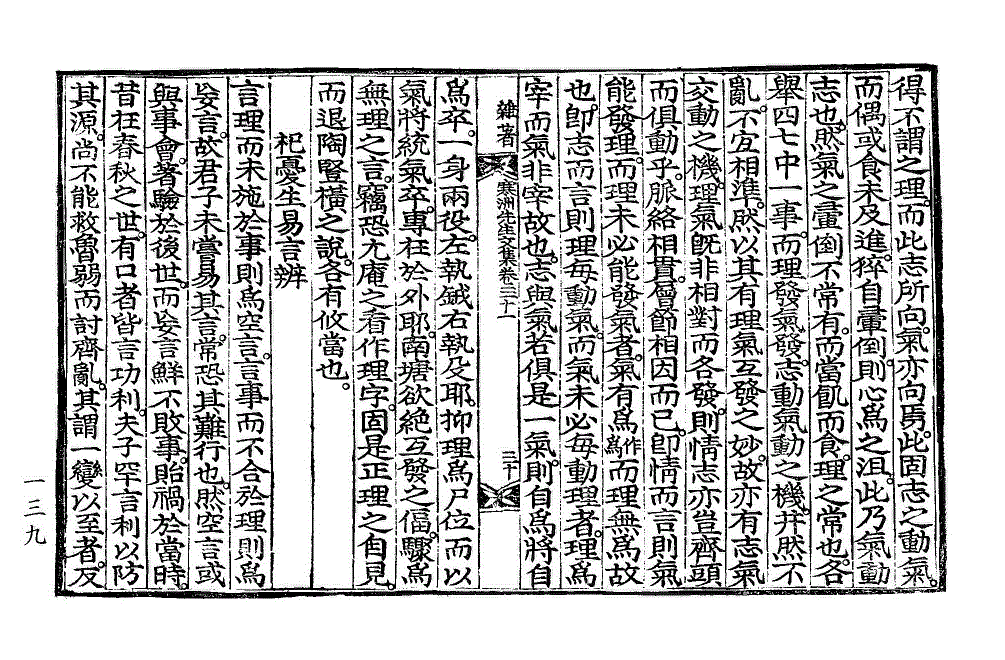 得不谓之理。而此志所向。气亦向焉。此固志之动气。而偶或食未及进。猝自晕倒。则心为之沮。此乃气动志也。然气之晕倒不常有。而当饥而食。理之常也。各举四七中一事。而理发气发。志动气动之机。井然不乱。不宜相准。然以其有理气互发之妙。故亦有志气交动之机。理气既非相对而各发。则情志亦岂齐头而俱动乎。脉络相贯。层节相因而已。即情而言则气能发理。而理未必能发气者。气有为(作为)而理无为故也。即志而言则理每动气。而气未必每动理者。理为宰而气非宰故也。志与气若俱是一气。则自为将自为卒。一身两役。左执钺右执殳耶。抑理为尸位而以气将统气卒。专在于外耶。南塘欲绝互发之偪。骤为无理之言。窃恐尤庵之看作理字。固是正理之自见。而退陶竖横之说。各有攸当也。
得不谓之理。而此志所向。气亦向焉。此固志之动气。而偶或食未及进。猝自晕倒。则心为之沮。此乃气动志也。然气之晕倒不常有。而当饥而食。理之常也。各举四七中一事。而理发气发。志动气动之机。井然不乱。不宜相准。然以其有理气互发之妙。故亦有志气交动之机。理气既非相对而各发。则情志亦岂齐头而俱动乎。脉络相贯。层节相因而已。即情而言则气能发理。而理未必能发气者。气有为(作为)而理无为故也。即志而言则理每动气。而气未必每动理者。理为宰而气非宰故也。志与气若俱是一气。则自为将自为卒。一身两役。左执钺右执殳耶。抑理为尸位而以气将统气卒。专在于外耶。南塘欲绝互发之偪。骤为无理之言。窃恐尤庵之看作理字。固是正理之自见。而退陶竖横之说。各有攸当也。祀忧生易言辨
言理而未施于事则为空言。言事而不合于理则为妄言。故君子未尝易其言。常恐其难行也。然空言或与事会。著验于后世。而妄言鲜不败事。贻祸于当时。昔在春秋之世。有口者皆言功利。夫子罕言利以防其源。尚不能救鲁弱而讨齐乱。其谓一变以至者。反
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40H 页
 为空言。然尚功利莫如齐。而去桓公未远。卒先鲁而亡于田氏。战国末功利之说益炽。李悝以土利。白圭以水利。孙吴以战伐。仪秦以从横。申韩以刑名。皆以为可致不世之功业。而孟子独以仁义之说。斥宋牼之利。卑管仲之功。其说不行。而天下遂大乱。卒见并于西戎之秦。秦以商鞅之变法致富强。招八州而朝同列。当是时。卫鞅为奇功。孟子为空言。而秦乃不旋踵而亡。此所谓帝秦亡秦。皆商鞅者也。汉以仁厚勤俭。安养其民。文景之业。庶几成康。及武帝时。鏖漠庭而槎河源。驾楼船而郡沧海。拓珠崖而田轮台。当其时董仲舒废处江都。大言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之所以不蹈秦辙。延至四百年所。未必非此一言扶护得国之元气也。晋置羌戎于塞内。不纳江统之言。驯致五胡之乱。拓跋宇文竟主夏盟。唐初称臣契丹。自为聚麀之夷风。而禄山沙陀至而遂亡之。宋之王安石以功利动神宗。青苗保甲之法。宜若致富强于一时。而毒痡四海。实阶徽钦北狩之祸。秦桧贾似道之属主和误国。苛敛虐民。遂亡于奇渥温之手。读经史谈治乱者。究观历代。亦可知功利之不足尚。华夷之不可混。而今此易言之书。
为空言。然尚功利莫如齐。而去桓公未远。卒先鲁而亡于田氏。战国末功利之说益炽。李悝以土利。白圭以水利。孙吴以战伐。仪秦以从横。申韩以刑名。皆以为可致不世之功业。而孟子独以仁义之说。斥宋牼之利。卑管仲之功。其说不行。而天下遂大乱。卒见并于西戎之秦。秦以商鞅之变法致富强。招八州而朝同列。当是时。卫鞅为奇功。孟子为空言。而秦乃不旋踵而亡。此所谓帝秦亡秦。皆商鞅者也。汉以仁厚勤俭。安养其民。文景之业。庶几成康。及武帝时。鏖漠庭而槎河源。驾楼船而郡沧海。拓珠崖而田轮台。当其时董仲舒废处江都。大言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之所以不蹈秦辙。延至四百年所。未必非此一言扶护得国之元气也。晋置羌戎于塞内。不纳江统之言。驯致五胡之乱。拓跋宇文竟主夏盟。唐初称臣契丹。自为聚麀之夷风。而禄山沙陀至而遂亡之。宋之王安石以功利动神宗。青苗保甲之法。宜若致富强于一时。而毒痡四海。实阶徽钦北狩之祸。秦桧贾似道之属主和误国。苛敛虐民。遂亡于奇渥温之手。读经史谈治乱者。究观历代。亦可知功利之不足尚。华夷之不可混。而今此易言之书。寒洲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第 140L 页
 都无一言及于仁义。而必曰用西法则利。合西法则不利。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彼王韬者衍说推奖。无复忌惮。傅之以孔子之言。跻之于孟子之功。噫噫痛矣。今有一队强盗。突入村坞。规占我田宅。使不得宁居。夺据我财产。使不得事育。攘窃我牺牲。使不得祭祀。其将号召宗族。收拾奴丁。严辞正名。逐盗坞外。而修墙屋固扃钥。申严防备。整顿家事。以为自全之计乎。抑将延盗于室。学盗之术。用饴沃枢。放火行劫。白昼剽金。黑夜胠箧。以求所谓富强可乎。今不独倡为不必攻讨之说。而直欲举华夏变于夷。此真朱子所谓乱贼之党。惜乎。其不见诛于春秋之法也。
都无一言及于仁义。而必曰用西法则利。合西法则不利。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彼王韬者衍说推奖。无复忌惮。傅之以孔子之言。跻之于孟子之功。噫噫痛矣。今有一队强盗。突入村坞。规占我田宅。使不得宁居。夺据我财产。使不得事育。攘窃我牺牲。使不得祭祀。其将号召宗族。收拾奴丁。严辞正名。逐盗坞外。而修墙屋固扃钥。申严防备。整顿家事。以为自全之计乎。抑将延盗于室。学盗之术。用饴沃枢。放火行劫。白昼剽金。黑夜胠箧。以求所谓富强可乎。今不独倡为不必攻讨之说。而直欲举华夏变于夷。此真朱子所谓乱贼之党。惜乎。其不见诛于春秋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