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书
书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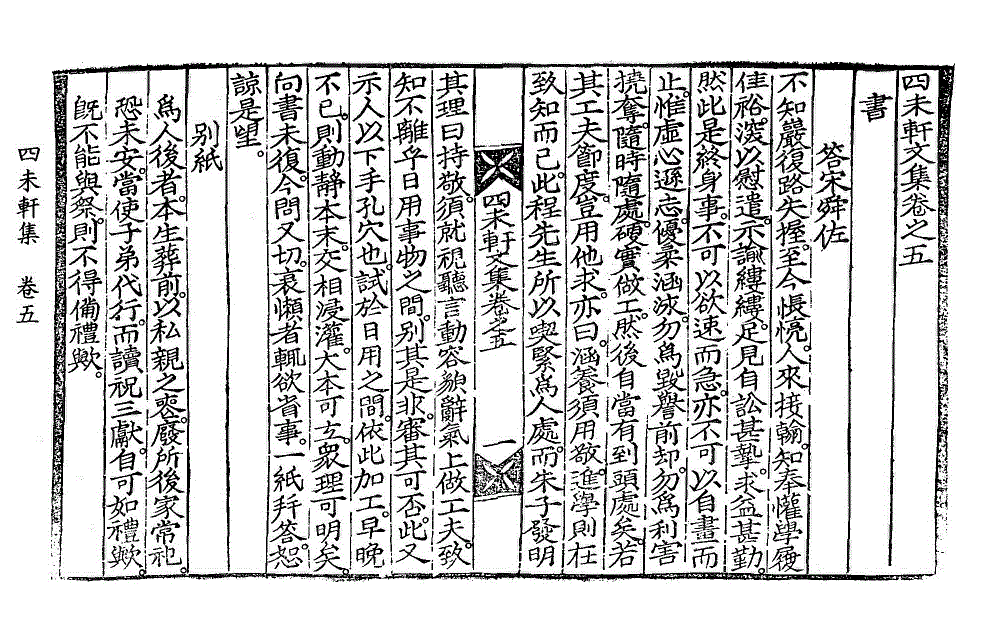 答宋舜佐
答宋舜佐不知岩复路失握。至今怅𢝋。人来接翰。知奉欢学履佳裕。深以慰遣。示谕缕缕。足见自讼甚挚。求益甚勤。然此是终身事。不可以欲速而急。亦不可以自画而止。惟虚心逊志。优柔涵泳。勿为毁誉前却。勿为利害挠夺。随时随处。硬实做工。然后自当有到头处矣。若其工夫节度。岂用他求。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已。此程先生所以吃紧为人处。而朱子发明其理曰持敬。须就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致知不离乎日用事物之间。别其是非。审其可否。此又示人以下手孔穴也。试于日用之间。依此加工。早晚不已。则动静本末。交相浸灌。大本可立。众理可明矣。向书未复。今问又切。衰懒者辄欲省事。一纸拜答。恕谅是望。
别纸
为人后者。本生葬前。以私亲之丧。废所后家常祀。恐未安。当使子弟代行。而读祝三献。自可如礼欤。既不能与祭。则不得备礼欤。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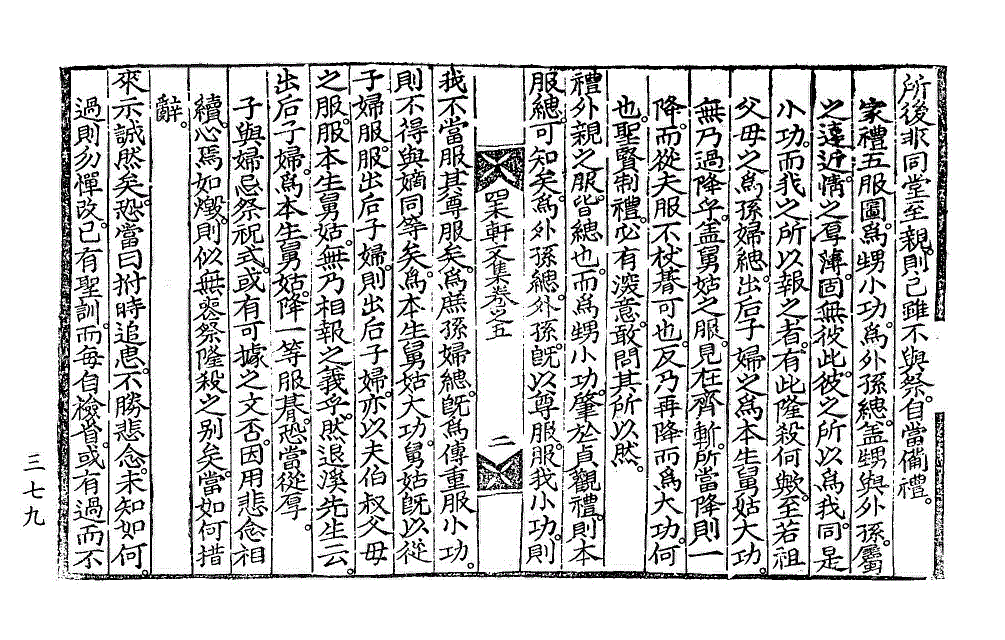 所后非同堂至亲。则已虽不与祭。自当备礼。
所后非同堂至亲。则已虽不与祭。自当备礼。家礼五服图。为甥小功。为外孙缌。盖甥与外孙。属之远近。情之厚薄。固无彼此。彼之所以为我。同是小功。而我之所以报之者。有此隆杀何欤。至若祖父母之为孙妇缌。出后子妇之为本生舅姑大功。无乃过降乎。盖舅姑之服。见在齐斩。所当降则一降。而从夫服不杖期可也。反乃再降而为大功。何也。圣贤制礼。必有深意。敢问其所以然。
礼外亲之服。皆缌也。而为甥小功。肇于贞观礼。则本服缌。可知矣。为外孙缌。外孙。既以尊服。服我小功。则我不当服其尊服矣。为庶孙妇缌。既为传重服小功。则不得与嫡同等矣。为本生舅姑大功。舅姑既以从子妇服。服出后子妇。则出后子妇。亦以夫伯叔父母之服。服本生舅姑。无乃相报之义乎。然退溪先生云。出后子妇。为本生舅姑。降一等服期。恐当从厚。
子与妇忌祭祝式。或有可据之文否。因用悲念相续。心焉如燬。则似无丧祭隆杀之别矣。当如何措辞。
来示诚然矣。恐当曰拊时追思。不胜悲念。未知如何。
过则勿惮改。已有圣训。而每自检省。或有过而不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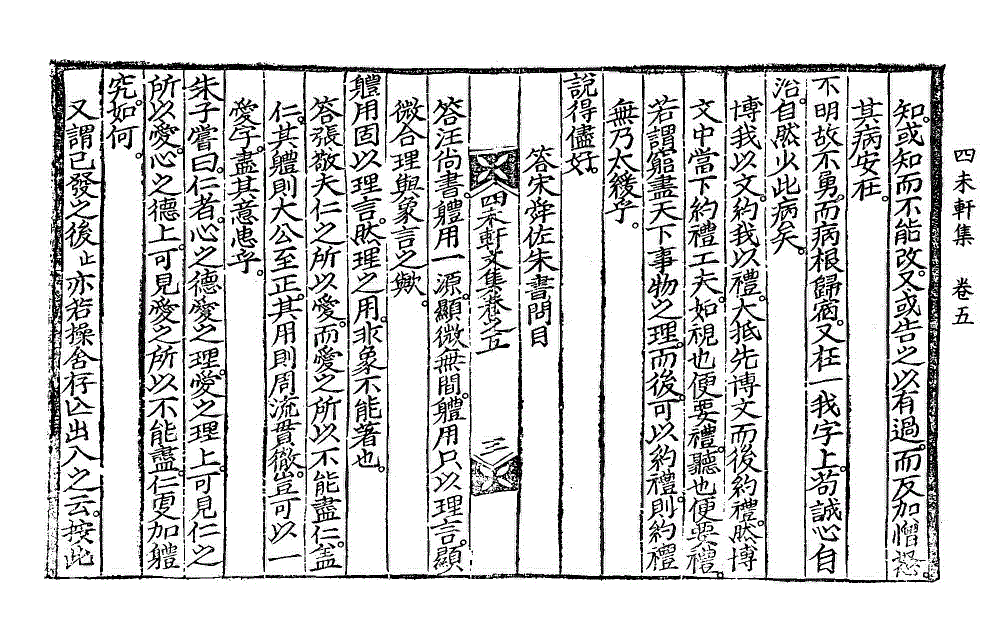 知。或知而不能改。又或告之以有过。而反加憎怒。其病安在。
知。或知而不能改。又或告之以有过。而反加憎怒。其病安在。不明故不勇。而病根归宿。又在一我字上。苟诚心自治。自然少此病矣。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大抵先博文而后约礼。然博文中当下约礼工夫。如视也便要礼。听也便要礼。若谓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而后。可以约礼。则约礼无乃太缓乎。
说得尽好。
答宋舜佐朱书问目
答汪尚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用只以理言。显微合理与象言之欤。
体用固以理言。然理之用。非象不能著也。
答张敬夫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盖仁。其体则大公至正。其用则周流贯彻。岂可以一爱字。尽其意思乎。
朱子尝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爱之理上。可见仁之所以爱。心之德上。可见爱之所以不能尽。仁更加体究。如何。
又谓已发之后(止)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按此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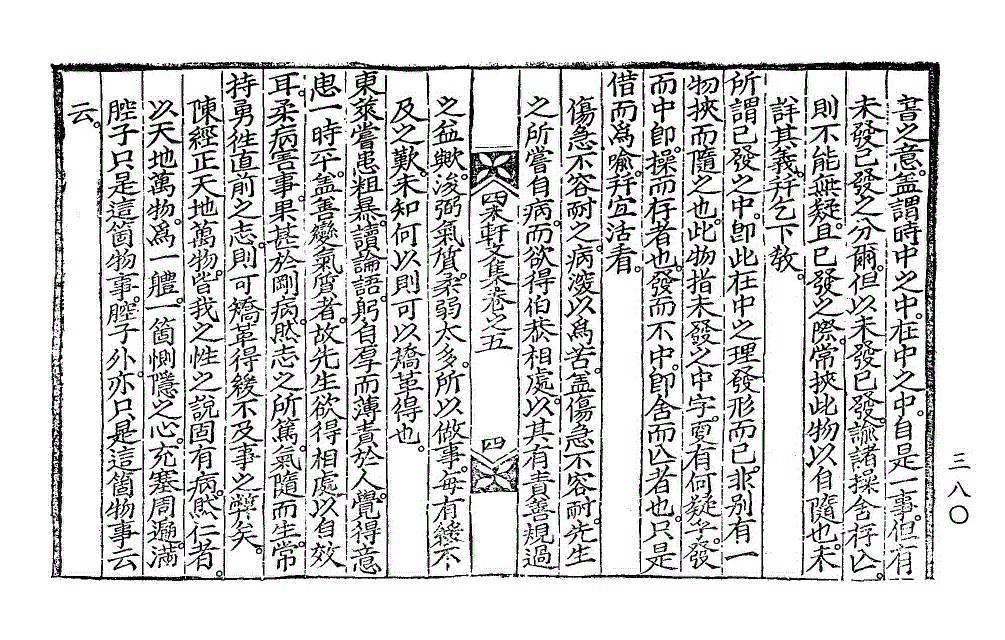 书之意。盖谓时中之中。在中之中。自是一事。但有未发已发之分尔。但以未发已发。谕诸操舍存亡。则不能无疑。且已发之际。常挟此物以自随也。未详其义。并乞下教。
书之意。盖谓时中之中。在中之中。自是一事。但有未发已发之分尔。但以未发已发。谕诸操舍存亡。则不能无疑。且已发之际。常挟此物以自随也。未详其义。并乞下教。所谓已发之中。即此在中之理发形而已。非别有一物挟而随之也。此物指未发之中字。更有何疑乎。发而中即。操而存者也。发而不中。即舍而亡者也。只是借而为喻。并宜活看。
伤急不容耐之。病深以为苦。盖伤急不容耐。先生之所尝自病。而欲得伯恭相处。以其有责善规过之益欤。浚弼气质。柔弱太多。所以做事。每有缓不及之叹。未知何以则可以矫革得也。
东莱尝患粗暴。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觉得意思一时平。盖善变气质者。故先生欲得相处以自效耳。柔病害事。果甚于刚病。然志之所笃。气随而生。常持勇往直前之志。则可矫革得缓不及事之弊矣。
陈经正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之说固有病。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个恻隐之心。充塞周遍。满腔子只是这个物事。腔子外。亦只是这个物事云云。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1H 页
 天地万物。固与我同体。然须将自己为主宰。见得物我一理。无有间隔。方是仁之实体。此夫子所以答子贡之问。必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张子西铭。必以吾字为原本者也。此书须以此意看破。不可泛以天地万物同体为仁。反涉莽荡之病也。
天地万物。固与我同体。然须将自己为主宰。见得物我一理。无有间隔。方是仁之实体。此夫子所以答子贡之问。必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张子西铭。必以吾字为原本者也。此书须以此意看破。不可泛以天地万物同体为仁。反涉莽荡之病也。论中和书。载于此篇者凡三。而首以仁字。为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中以道字。为未发已发之全体。终以心字。为中和之纲领。前后开发不一。敢问其义。
朱子不曰中和之妙。须以心为主乎。更思之如何。
周子之言主静。就中正仁义而言。盖此书。以中仁为静。正义为动。太极图说解。以中仁为动。正义为静。其相为体用之义。愿闻之。
指未发之中全体之仁。则中仁属静。指处物之宜。处事之正。则正义属动。故曰以中对正。中为重。以义配仁。仁为本。然论性答稿以为中仁阳故属动。正义阴故属静。实得图说本意也。其各有体用。互为体用之说。详见退陶先生答李艮斋书。幸检看也。
答裴章之(灿)
向谕以古人毋自暴弃之训。为变化气质之方。此诚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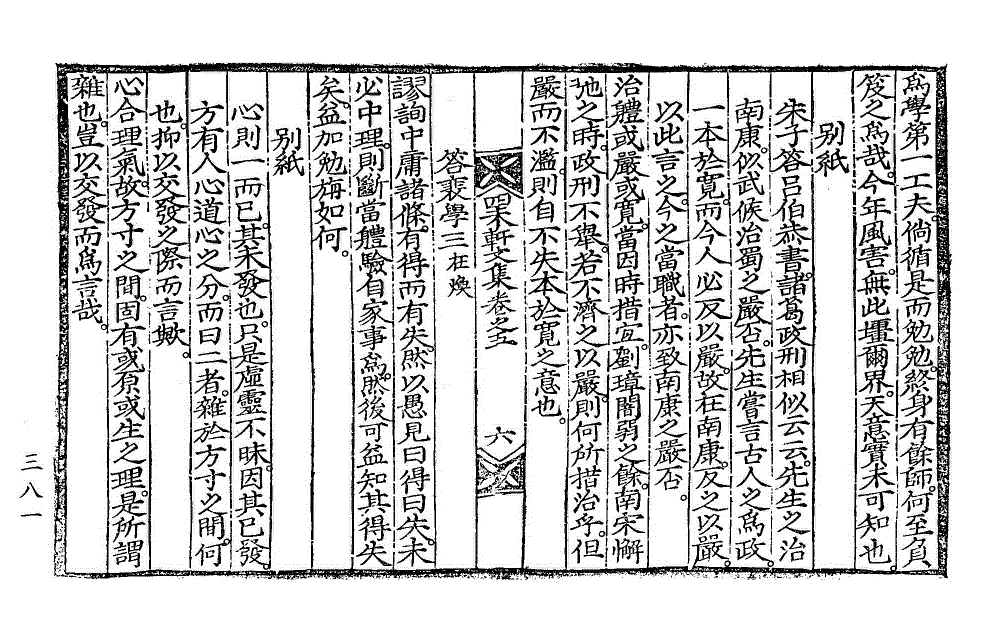 为学第一工夫。倘循是而勉勉。终身有馀师。何至负笈之为哉。今年风害。无此疆尔界。天意实未可知也。
为学第一工夫。倘循是而勉勉。终身有馀师。何至负笈之为哉。今年风害。无此疆尔界。天意实未可知也。别纸
朱子答吕伯恭书。诸葛政刑相似云云。先生之治南康。似武候治蜀之严否。先生尝言古人之为政。一本于宽。而今人必反以严。故在南康。反之以严。以此言之。今之当职者。亦致南康之严否。
治体或严或宽。当因时措宜。刘璋闇弱之馀。南宋懈弛之时。政刑不举。若不济之以严。则何所措治乎。但严而不滥。则自不失本于宽之意也。
答裴学三(在焕)
谬询中庸诸条。有得而有失。然以愚见曰得曰失。未必中理。则断当体验自家事为。然后可益知其得失矣。益加勉旃如何。
别纸
心则一而已。其未发也。只是虚灵不昧。因其已发。方有人心道心之分。而曰二者。杂于方寸之间。何也。抑以交发之际而言欤。
心合理气。故方寸之间。固有或原或生之理。是所谓杂也。岂以交发而为言哉。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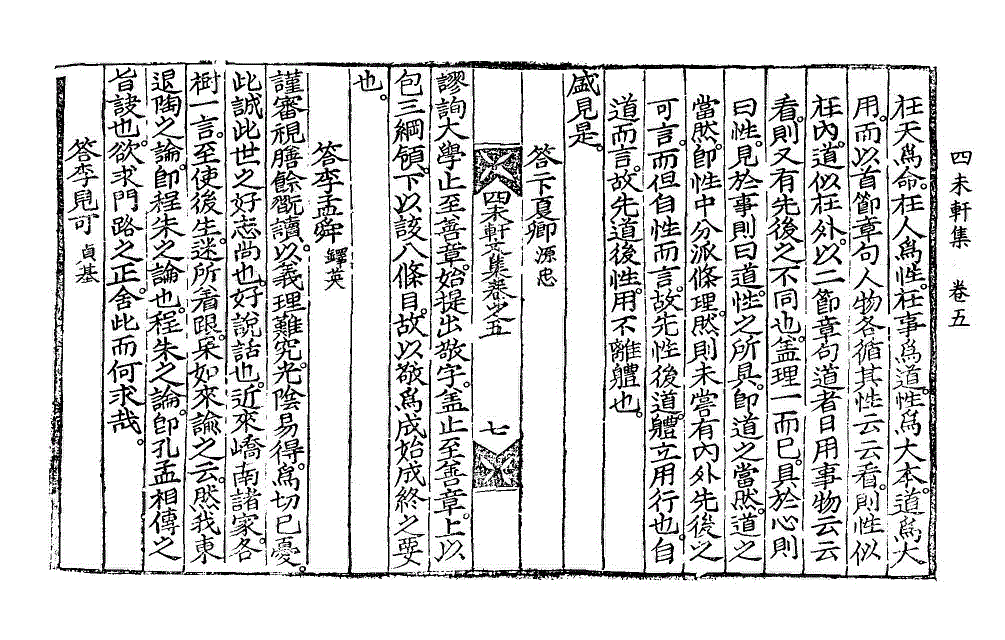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事为道。性为大本。道为大用。而以首节章句人物各循其性云云看。则性似在内。道似在外。以二节章句道者日用事物云云看。则又有先后之不同也。盖理一而已。具于心则曰性。见于事则曰道。性之所具。即道之当然。道之当然。即性中分派条理。然则未尝有内外先后之可言。而但自性而言。故先性后道。体立用行也。自道而言。故先道后性。用不离体也。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事为道。性为大本。道为大用。而以首节章句人物各循其性云云看。则性似在内。道似在外。以二节章句道者日用事物云云看。则又有先后之不同也。盖理一而已。具于心则曰性。见于事则曰道。性之所具。即道之当然。道之当然。即性中分派条理。然则未尝有内外先后之可言。而但自性而言。故先性后道。体立用行也。自道而言。故先道后性。用不离体也。盛见是。
答卞夏卿(源忠)
谬询大学止至善章。始提出敬字。盖止至善章。上以包三纲领。下以该八条目。故以敬为成始成终之要也。
答李孟舜(铎英)
谨审视膳馀玩读。以义理难究。光阴易得。为切己忧。此诚此世之好志尚也。好说话也。近来峤南诸家。各树一言。至使后生。迷所着跟。果如来谕之云。然我东退陶之论。即程朱之论也。程朱之论。即孔孟相传之旨诀也。欲求门路之正。舍此而何求哉。
答李见可(贞基)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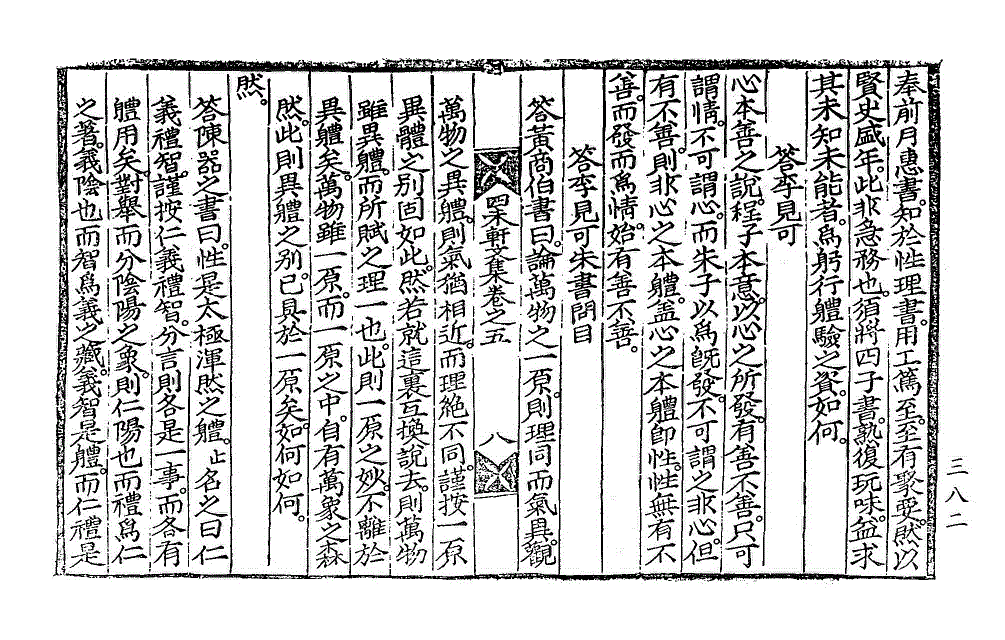 奉前月惠书。知于性理书。用工笃至。至有聚要。然以贤史盛年。此非急务也。须将四子书。熟复玩味。益求其未知未能者。为躬行体验之资。如何。
奉前月惠书。知于性理书。用工笃至。至有聚要。然以贤史盛年。此非急务也。须将四子书。熟复玩味。益求其未知未能者。为躬行体验之资。如何。答李见可
心本善之说。程子本意。以心之所发。有善不善。只可谓情。不可谓心。而朱子以为既发。不可谓之非心。但有不善。则非心之本体。盖心之本体即性。性无有不善。而发而为情。始有善不善。
答李见可朱书问目
答黄商伯书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谨按一原异体之别固如此。然若就这里互换说去。则万物虽异体。而所赋之理一也。此则一原之妙。不离于异体矣。万物虽一原。而一原之中。自有万象之森然。此则异体之别。已具于一原矣。如何如何。
然。
答陈器之书曰。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止)名之曰仁义礼智。谨按仁义礼智。分言则各是一事。而各有体用矣。对举而分阴阳之象。则仁阳也而礼为仁之著。义阴也而智为义之藏。义智是体。而仁礼是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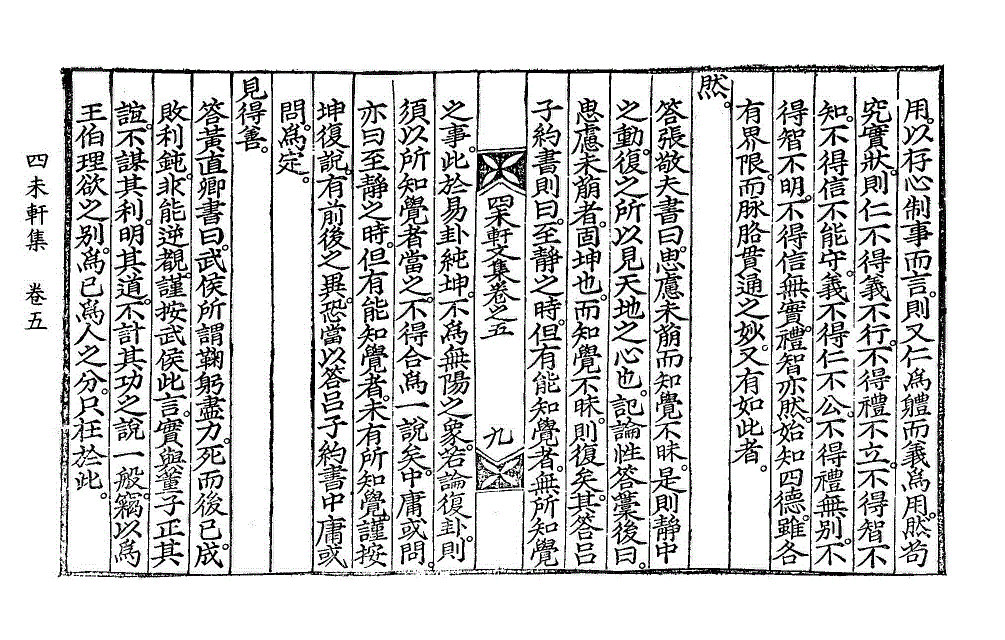 用。以存心制事而言。则又仁为体而义为用。然苟究实状。则仁不得义不行。不得礼不立。不得智不知。不得信不能守。义不得仁不公。不得礼无别。不得智不明。不得信无实。礼智亦然。始知四德。虽各有界限。而脉胳贯通之妙。又有如此者。
用。以存心制事而言。则又仁为体而义为用。然苟究实状。则仁不得义不行。不得礼不立。不得智不知。不得信不能守。义不得仁不公。不得礼无别。不得智不明。不得信无实。礼智亦然。始知四德。虽各有界限。而脉胳贯通之妙。又有如此者。然。
答张敬夫书曰。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记论性答稿后曰。思虑未萌者。固坤也。而知觉不昧。则复矣。其答吕子约书则曰。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觉者。无所知觉之事。此于易卦纯坤。不为无阳之象。若论复卦。则须以所知觉者当之。不得合为一说矣。中庸或问。亦曰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觉者。未有所知觉。谨按坤复说。有前后之异。恐当以答吕子约书中庸或问。为定。
见得善。
答黄直卿书曰。武侯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能逆睹。谨按武侯此言。实与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一般。窃以为王伯理欲之别。为己为人之分。只在于此。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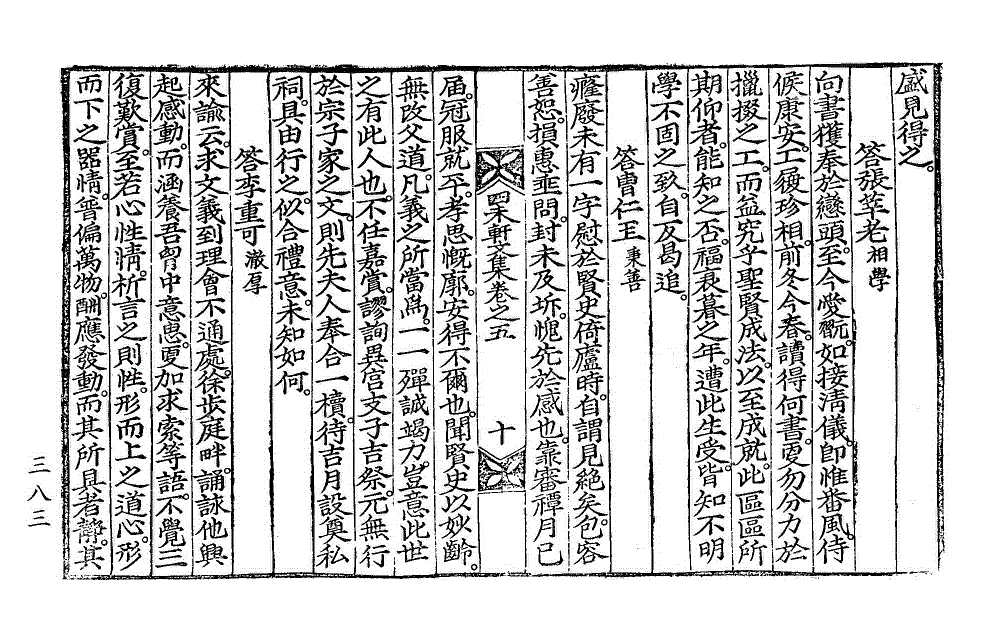 盛见得之。
盛见得之。答张莘老(相学)
向书获奉于恋头。至今爱玩。如接清仪。即惟番风。侍候康安。工履珍相。前冬今春。读得何书。更勿分力于擸掇之工。而益究乎圣贤成法。以至成就。此区区所期仰者。能知之否。福衰暮之年。遭此生受。皆知不明学不固之致。自反曷追。
答曹仁玉(秉善)
癃废未有一字慰于贤史倚庐时。自谓见绝矣。包容善恕。损惠垂问。封未及坼。愧先于感也。靠审禫月已届。冠服就平。孝思慨廓。安得不尔也。闻贤史以妙龄。无改父道。凡义之所当为。一一殚诚竭力。岂意此世之有此人也。不任嘉赏。谬询异宫支子吉祭。元无行于宗子家之文。则先夫人奉合一椟。待吉月设奠私祠。具由行之。似合礼意。未知如何。
答李重可(澈厚)
来谕云。求文义到理会不通处。徐步庭畔。诵咏他兴起感动。而涵养吾胸中意思。更加求索等语。不觉三复叹赏。至若心性情。析言之则性。形而上之道心。形而下之器情。普偏万物。酬应发动。而其所具者静。其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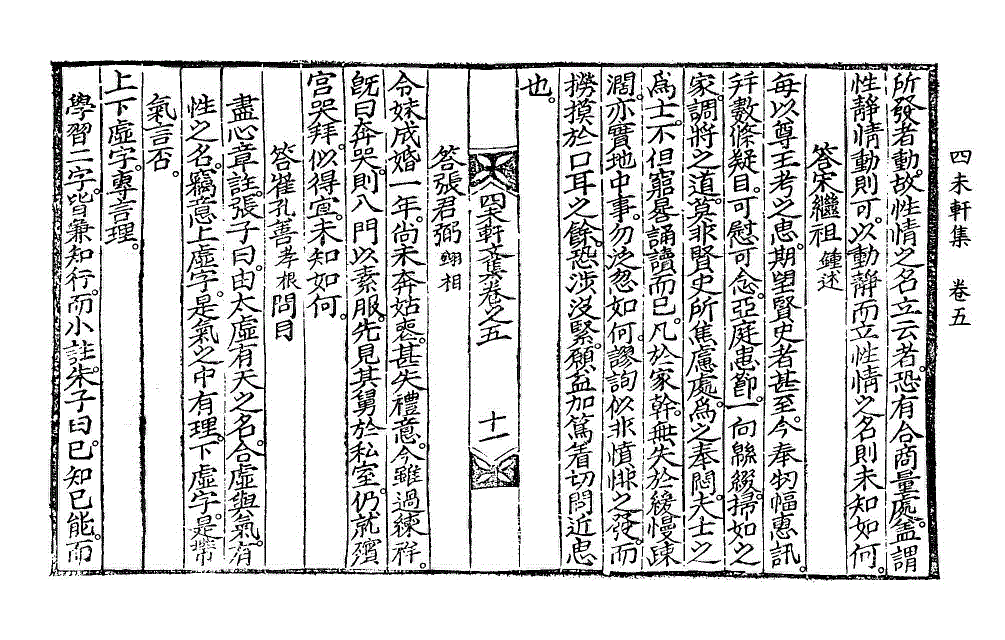 所发者动。故性情之名立云者。恐有合商量处。盖谓性静情动则可。以动静而立性情之名则未知如何。
所发者动。故性情之名立云者。恐有合商量处。盖谓性静情动则可。以动静而立性情之名则未知如何。答宋继祖(钟述)
每以尊王考之思。期望贤史者甚至。今奉牣幅惠讯。并数条疑目。可慰可念。亚庭患节。一向绵缀。扫如之家。调将之道。莫非贤史所焦虑处。为之奉闷。夫士之为士。不但穷晷诵读而已。凡于家干。无失于缓慢疏阔。亦实地中事。勿泛忽如何。谬询似非愤悱之发。而捞摸于口耳之馀。恐涉没紧。愿益加笃着切问近思也。
答张君弼(翊相)
令妹成婚一年。尚未奔姑丧。甚失礼意。今虽过练祥。既曰奔哭。则入门以素服。先见其舅于私室。仍就殡宫哭拜。似得宜。未知如何。
答崔孔善(孝根)问目
尽心章注。张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窃意上虚字。是气之中有理。下虚字。是带气言否。
上下虚字。专言理。
学习二字。皆兼知行。而小注。朱子曰。已知已能。而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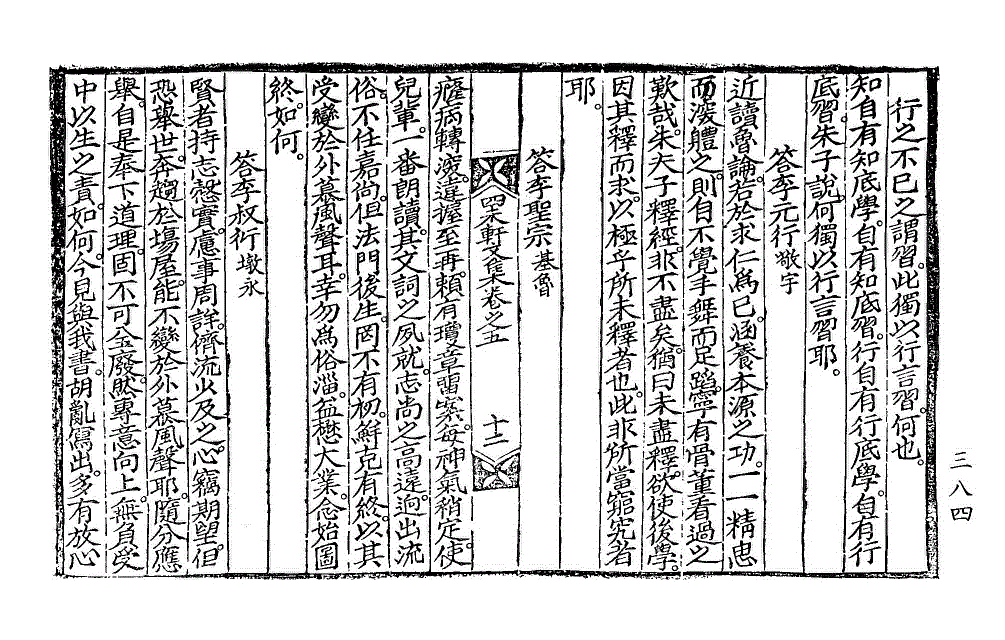 行之不已之谓习。此独以行言习。何也。
行之不已之谓习。此独以行言习。何也。知自有知底学。自有知底习。行自有行底学。自有行底习。朱子说。何独以行言习耶。
答李元行(敬宇)
近读鲁论。若于求仁为己。涵养本源之功。一一精思而深体之。则自不觉手舞而足蹈。宁有骨董看过之叹哉。朱夫子释经。非不尽矣。犹曰未尽释。欲使后学。因其释而求。以极乎所未释者也。此非所当穷究者耶。
答李圣宗(基鲁)
癃病转深。违握至再。赖有琼章留案。每神气稍定。使儿辈。一番朝读。其文词之夙就。志尚之高远。迥出流俗。不任嘉尚。但法门后生。罔不有初。鲜克有终。以其受变于外慕风声耳。幸勿为俗淄。益懋大业。念始图终。如何。
答李叔衍(墩永)
贤者持志悫实。虑事周详。侪流少及之。心窃期望。但恐举世。奔趋于场屋。能不变于外慕风声耶。随分应举。自是奉下道理。固不可全废。然专意向上。无负受中以生之责。如何。今见与我书。胡乱写出。多有放心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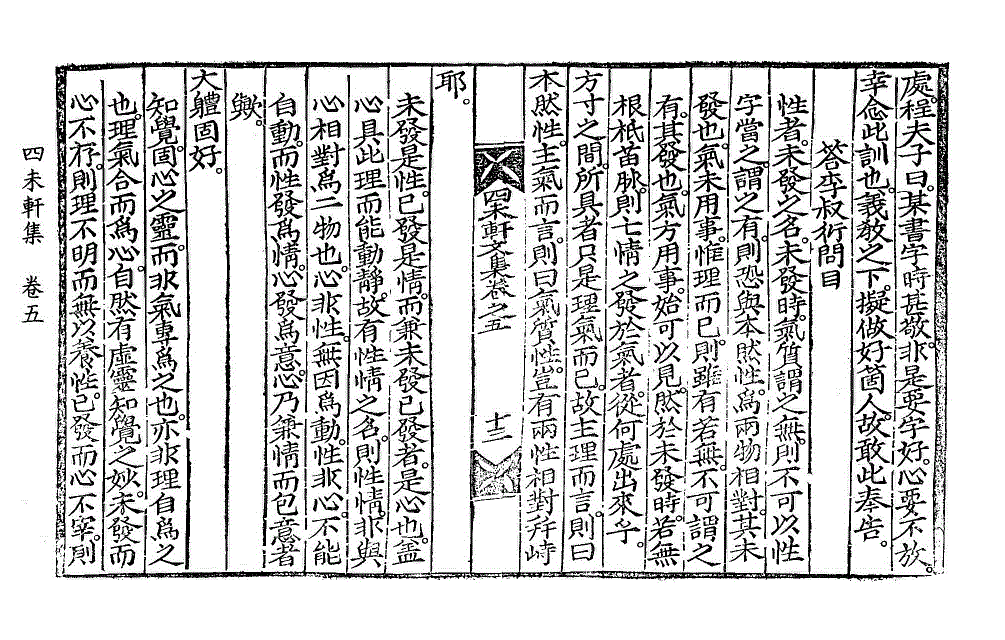 处。程夫子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心要不放。幸念此训也。义教之下。拟做好个人。故敢此奉告。
处。程夫子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心要不放。幸念此训也。义教之下。拟做好个人。故敢此奉告。答李叔衍问目
性者。未发之名。未发时。气质谓之无。则不可以性字当之。谓之有。则恐与本然性。为两物相对。其未发也。气未用事。惟理而已。则虽有若无。不可谓之有。其发也。气方用事。始可以见。然于未发时。若无根柢苗脉。则七情之发于气者。从何处出来乎。
方寸之间。所具者只是理气而已。故主理而言。则曰本然性。主气而言。则曰气质性。岂有两性相对并峙耶。
未发是性。已发是情。而兼未发已发者。是心也。盖心具此理而能动静。故有性情之名。则性情。非与心相对为二物也。心非性。无因为动。性非心。不能自动。而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心乃兼情而包意者欤。
大体固好。
知觉。固心之灵。而非气专为之也。亦非理自为之也。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未发而心不存。则理不明而无以养性。已发而心不宰。则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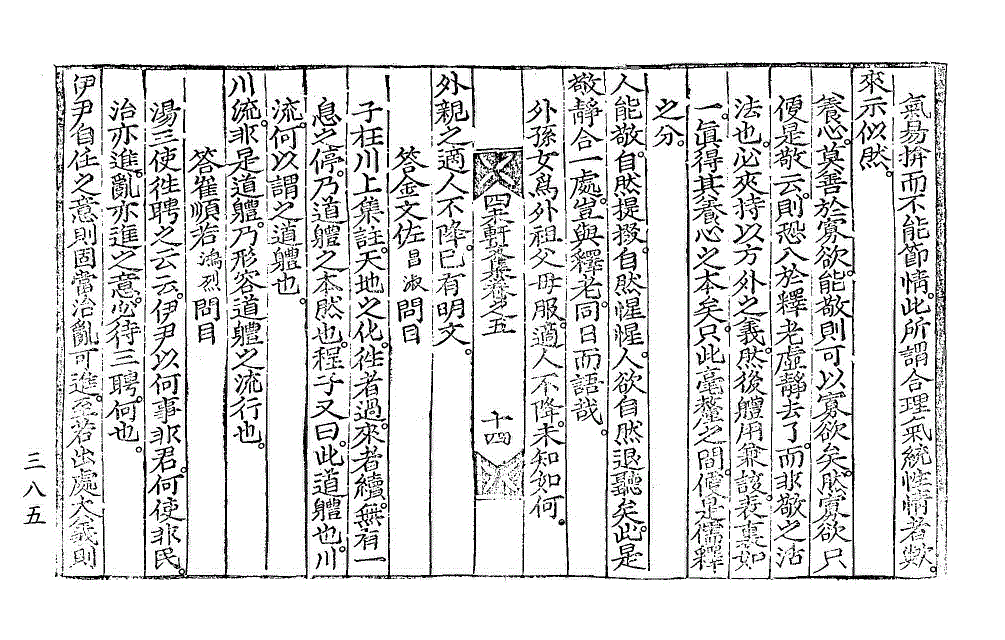 气易掩而不能节情。此所谓合理气统性情者欤。
气易掩而不能节情。此所谓合理气统性情者欤。来示似然。
养心。莫善于寡欲。能敬则可以寡欲矣。然寡欲只便是敬云。则恐入于释老虚静去了。而非敬之活法也。必夹持以方外之义。然后体用兼该。表里如一。真得其养心之本矣。只此毫釐之间。便是儒释之分。
人能敬。自然提掇。自然惺惺。人欲自然退听矣。此是敬静合一处。岂与释老。同日而语哉。
外孙女为外祖父母服。适人不降。未知如何。
外亲之适人不降。已有明文。
答金文佐(昌淑)问目
子在川上集注。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有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程子又曰。此道体也。川流。何以谓之道体也。
川流。非是道体。乃形容道体之流行也。
答崔顺若(鸿烈)问目
汤三使往聘之云云。伊尹以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之意。必待三聘。何也。
伊尹自任之意则固当治乱可进。至若出处大义则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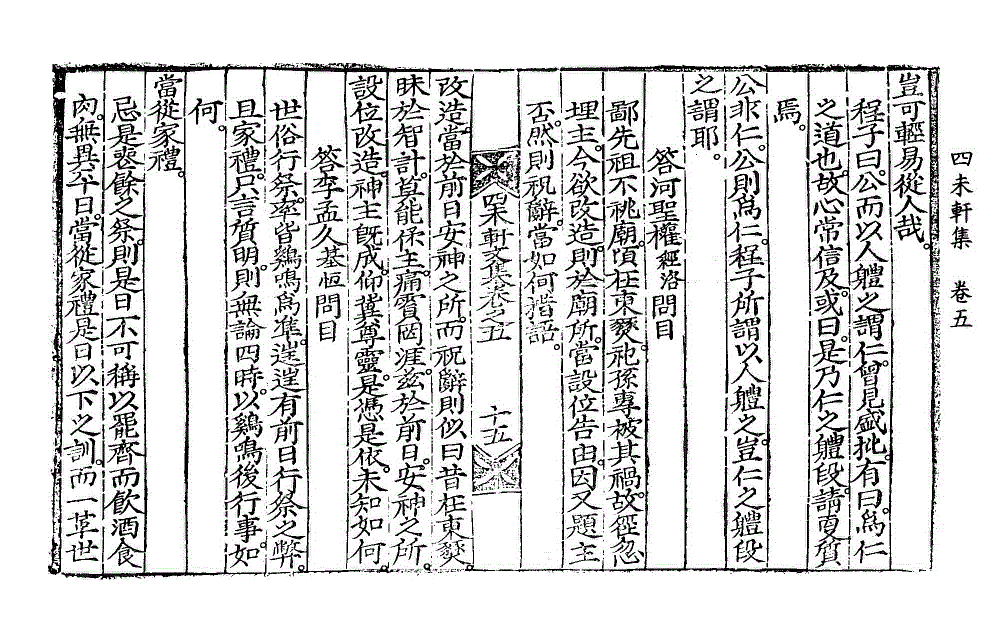 岂可轻易从人哉。
岂可轻易从人哉。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谓仁。曾见盛批。有曰。为仁之道也。故心常信及。或曰。是乃仁之体段。请更质焉。
公非仁。公则为仁。程子所谓以人体之。岂仁之体段之谓耶。
答河圣权(经洛)问目
鄙先祖不祧庙。顷在东燹。祀孙专被其祸。故径忽埋主。今欲改造。则于庙所。当设位告由。因又题主否。然则祝辞。当如何措语。
改造。当于前日安神之所。而祝辞则似曰昔在东燹。昧于智计。莫能保主。痛霣罔涯。玆于前日。安神之所。设位改造。神主既成。仰冀尊灵。是凭是依。未知如何。
答李孟久(基恒)问目
世俗行祭。率皆鸡鸣为准。𨓏𨓏有前日行祭之弊。且家礼。只言质明。则无论四时。以鸡鸣后行事。如何。
当从家礼。
忌是丧馀之祭。则是日不可称以罢齐而饮酒食肉。无异平日。当从家礼是日以下之训。而一革世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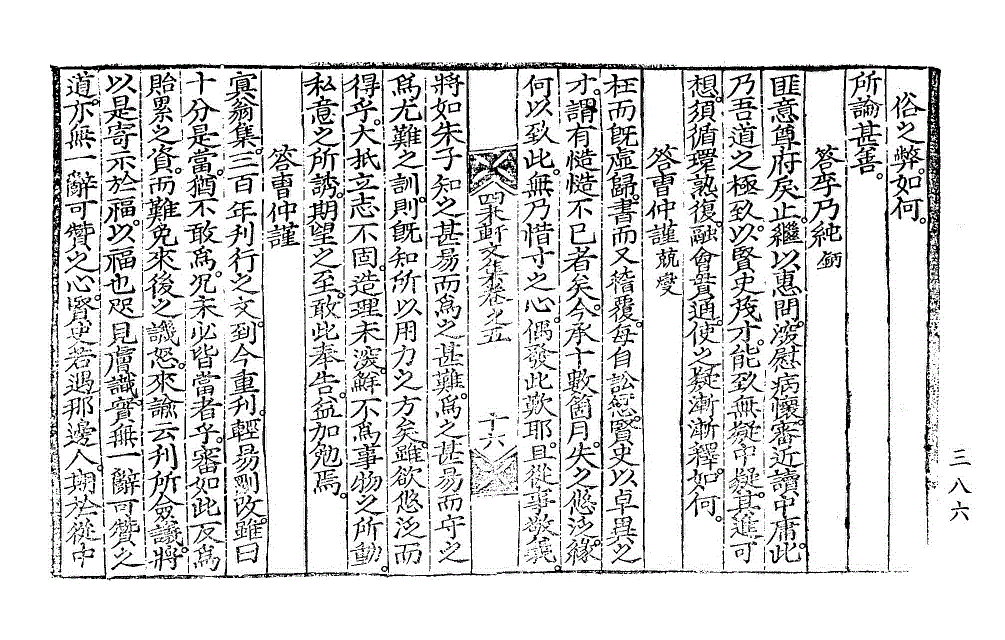 俗之弊。如何。
俗之弊。如何。所论甚善。
答李乃纯(鈵)
匪意尊府戾止。继以惠问。深慰病怀。审近读中庸。此乃吾道之极致。以贤史茂才。能致无疑中疑。其进可想。须循环熟复。融会贯通。使之疑渐渐释。如何。
答曹仲谨(兢燮)
在而既虚归。书而又稽覆。每自讼愆。贤史以卓异之才。谓有慥慥不已者矣。今承十数个月。失之悠泛。缘何以致此。无乃惜寸之心。偶发此叹耶。且从事敬义。将如朱子知之甚易而为之甚难。为之甚易而守之为尤难之训。则既知所以用力之方矣。虽欲悠泛而得乎。大抵立志不固。造理未深。鲜不为事物之所动。私意之所诱。期望之至。敢此奉告。益加勉焉。
答曹仲谨
冥翁集。三百年刊行之文。到今重刊。轻易删改。虽曰十分是当。犹不敢为。况未必皆当者乎。审如此反为贻累之资。而难免来后之讥怒。来谕云刊所佥议。将以是寄示于福。以福也咫见肤识。实无一辞可赞之道。亦无一辞可赞之心。贤史若遇那边人。期于从中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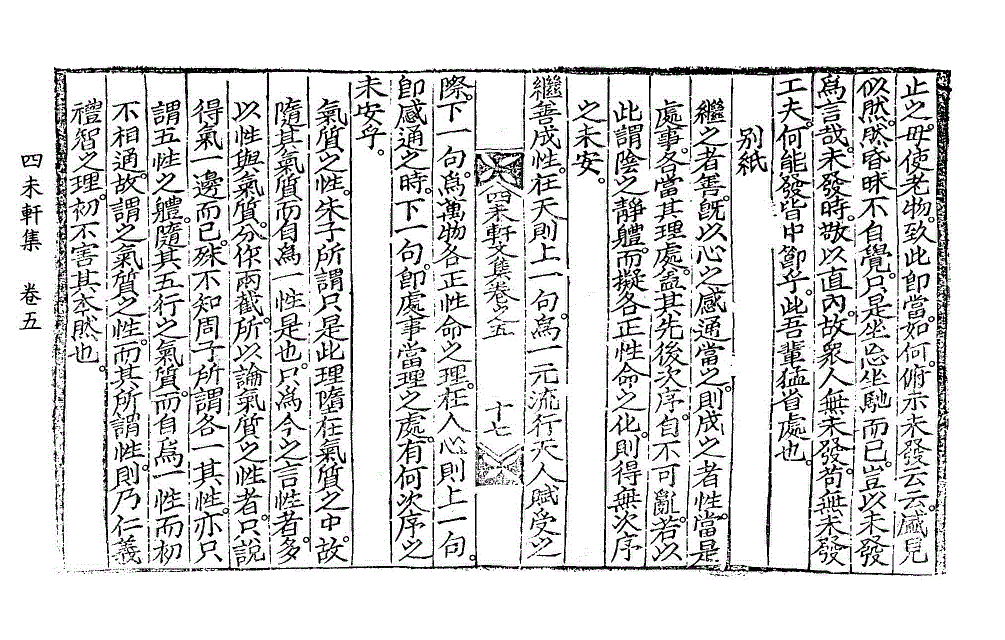 止之。毋使老物。致此即当。如何。俯示未发云云。盛见似然。然昏昧不自觉。只是坐忘坐驰而已。岂以未发为言哉。未发时。敬以直内。故众人无未发。苟无未发工夫。何能发皆中节乎。此吾辈猛省处也。
止之。毋使老物。致此即当。如何。俯示未发云云。盛见似然。然昏昧不自觉。只是坐忘坐驰而已。岂以未发为言哉。未发时。敬以直内。故众人无未发。苟无未发工夫。何能发皆中节乎。此吾辈猛省处也。别纸
继之者善。既以心之感通当之。则成之者性。当是处事。各当其理处。盖其先后次序。自不可乱。若以此谓阴之静体。而拟各正性命之化。则得无次序之未安。
继善成性。在天则上一句。为一元流行天人赋受之际。下一句。为万物各正性命之理。在人心则上一句。即感通之时。下一句。即处事当理之处。有何次序之未安乎。
气质之性。朱子所谓只是此理堕在气质之中。故随其气质而自为一性是也。只为今之言性者。多以性与气质。分作两截。所以论气质之性者。只说得气一边而已。殊不知周子所谓各一其性。亦只谓五性之体。随其五行之气质。而自为一性而初不相通。故谓之气质之性。而其所谓性。则乃仁义礼智之理。初不害其本然也。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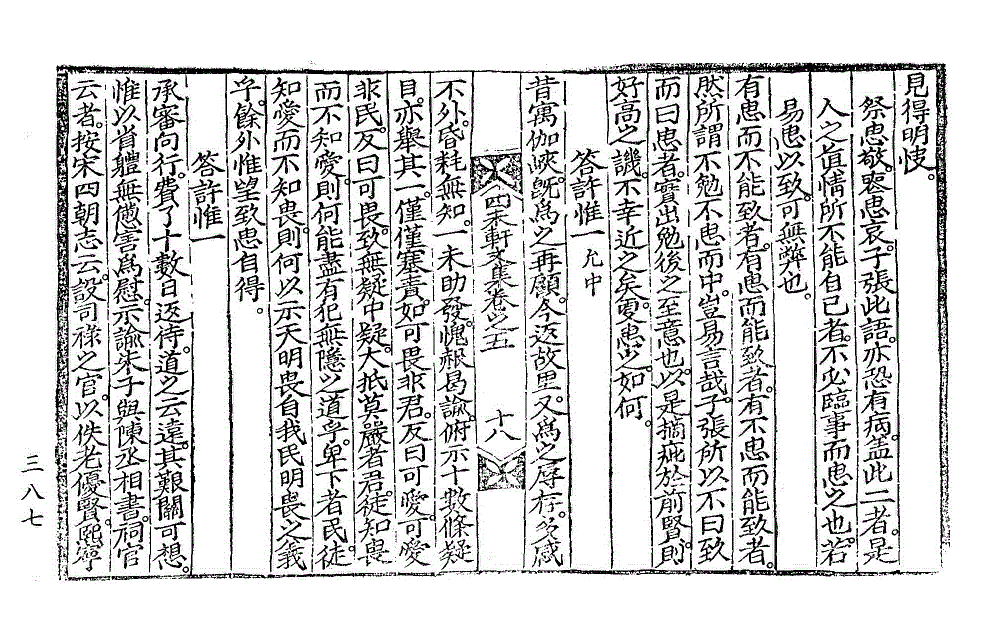 见得明快。
见得明快。祭思敬。丧思哀。子张此语。亦恐有病。盖此二者。是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不必临事而思之也。若易思以致。可无弊也。
有思而不能致者。有思而能致者。有不思而能致者。然所谓不勉不思而中。岂易言哉。子张所以不曰致而曰思者。实出勉后之至意也。以是摘疵于前贤。则好高之讥。不幸近之矣。更思之。如何。
答许惟一(允中)
昔寓伽峡。既为之再顾。今返故里。又为之辱存。多感不外。昏耗无知。一未助发。愧赧曷谕。俯示十数条疑目。亦举其一。仅仅塞责。如可畏非君。反曰可爱。可爱非民。反曰可畏。致无疑中疑。大抵莫严者君。徒知畏而不知爱。则何能尽有犯无隐之道乎。卑下者民。徒知爱而不知畏。则何以示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之义乎。馀外惟望致思自得。
答许惟一
承审向行。费了十数日返侍。道之云远。其艰关可想。惟以省体无惫害为慰。示谕朱子与陈丞相书。祠官云者。按宋四朝志云。设司禄之官。以佚老优贤。熙宁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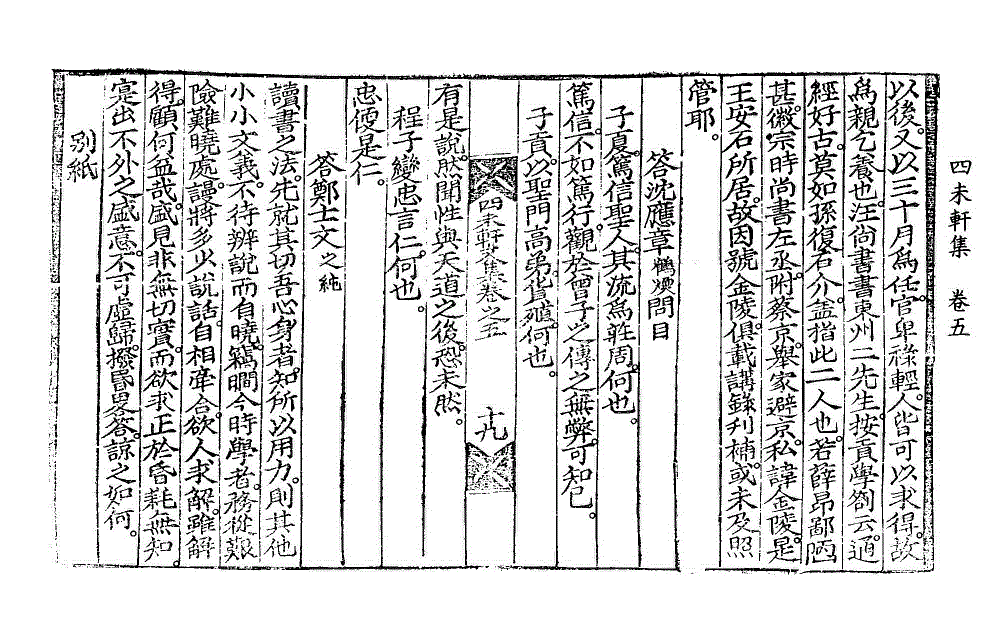 以后。又以三十月为任。官卑禄轻。人皆可以求得。故为亲乞养也。汪尚书书东州二先生。按贡学劄云。通经好古。莫如孙复石介。盖指此二人也。若薛昂鄙陋甚。徽宗时尚书左丞。附蔡京。举家避京。私讳金陵。是王安石所居。故因号金陵。俱载讲录刊补。或未及照管耶。
以后。又以三十月为任。官卑禄轻。人皆可以求得。故为亲乞养也。汪尚书书东州二先生。按贡学劄云。通经好古。莫如孙复石介。盖指此二人也。若薛昂鄙陋甚。徽宗时尚书左丞。附蔡京。举家避京。私讳金陵。是王安石所居。故因号金陵。俱载讲录刊补。或未及照管耶。答沈应章(鹤焕)问目
子夏。笃信圣人。其流为庄周。何也。
笃信。不如笃行。观于曾子之传之无弊。可知已。
子贡。以圣门高弟。货殖。何也。
有是说。然闻性与天道之后。恐未然。
程子变忠言仁。何也。
忠便是仁。
答郑士文(之纯)
读书之法。先就其切吾心身者。知所以用力。则其他小小文义。不待辨说而自晓。窃瞷今时学者。务从艰险难晓处。谩将多少说话。自相牵合。欲人求解。虽解得。顾何益哉。盛见非无切实。而欲求正于昏耗无知。寔出不外之盛意。不可虚归。拨昏略答。谅之如何。
别纸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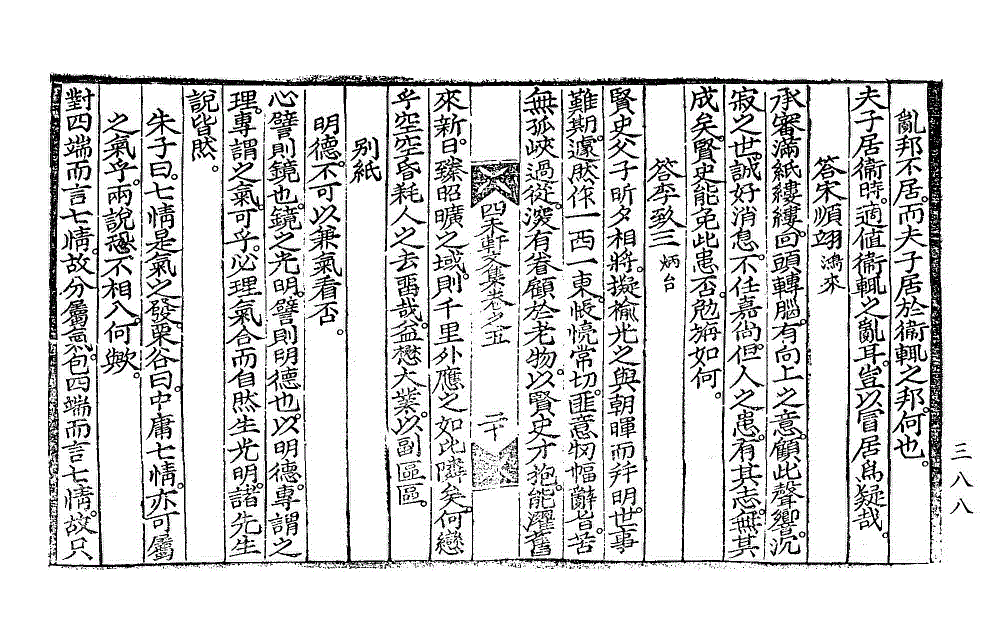 乱邦不居。而夫子居于卫辄之邦。何也。
乱邦不居。而夫子居于卫辄之邦。何也。夫子居卫时。适值卫辄之乱耳。岂以冒居为疑哉。
答宋顺翊(鸿来)
承审满纸缕缕。回头转脑。有向上之意。顾此声响。沉寂之世。诚好消息。不任嘉尚。但人之患。有其志。无其成矣。贤史能免此患否。勉旃如何。
答李致三(炳台)
贤史父子昕夕相将。拟榆光之与朝晖而并明。世事难期。遽然作一西一东。怅𢝋常切。匪意牣幅辞旨。苦无孤峡过从。深有眷顾于老物。以贤史才抱。能濯旧来新。日臻昭旷之域。则千里外应之如比邻矣。何恋乎空空昏耗人之去留哉。益懋大业。以副区区。
别纸
明德。不可以兼气看否。
心譬则镜也。镜之光明。譬则明德也。以明德。专谓之理。专谓之气。可乎。必理气合而自然生光明。诸先生说皆然。
朱子曰。七情是气之发。栗谷曰。中庸七情。亦可属之气乎。两说恐不相入。何欤。
对四端而言七情。故分属气。包四端而言七情。故只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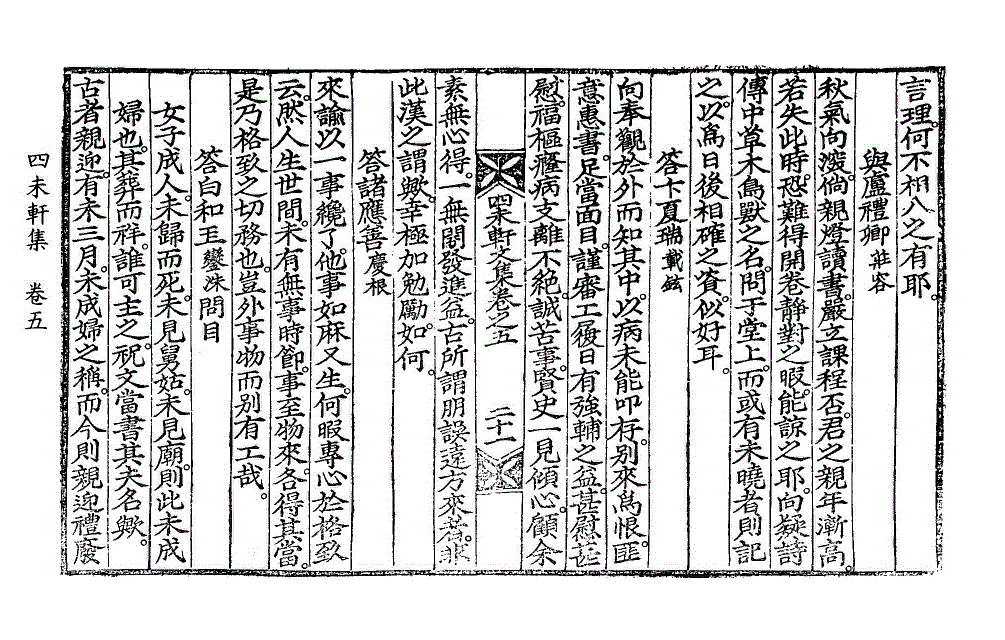 言理。何不相入之有耶。
言理。何不相入之有耶。与卢礼卿(庄容)
秋气向深。倘亲灯读书。严立课程否。君之亲年渐高。若失此时。恐难得开卷静对之暇。能谅之耶。向疑诗传中草木鸟兽之名。问于堂上。而或有未晓者则记之。以为日后相确之资。似好耳。
答卞夏瑞(载铉)
向奉观于外而知其中。以病未能叩存。别来为恨。匪意惠书。足当面目。谨审工履日有强辅之益。甚慰甚慰。福枢癃病支离不绝。诚苦事。贤史一见倾心。顾余素无心得。一无开发进益。古所谓朋误远方来者。非此汉之谓欤。幸极加勉励。如何。
答诸应善(庆根)
来谕以一事才了。他事如麻又生。何暇专心于格致云。然人生世间。未有无事时节。事至物来。各得其当。是乃格致之切务也。岂外事物而别有工哉。
答白和玉(銮洙)问目
女子成人。未归而死。未见舅姑。未见庙。则此未成妇也。其葬而祥。谁可主之。祝文当书其夫名欤。
古者亲迎。有未三月。未成妇之称。而今则亲迎礼废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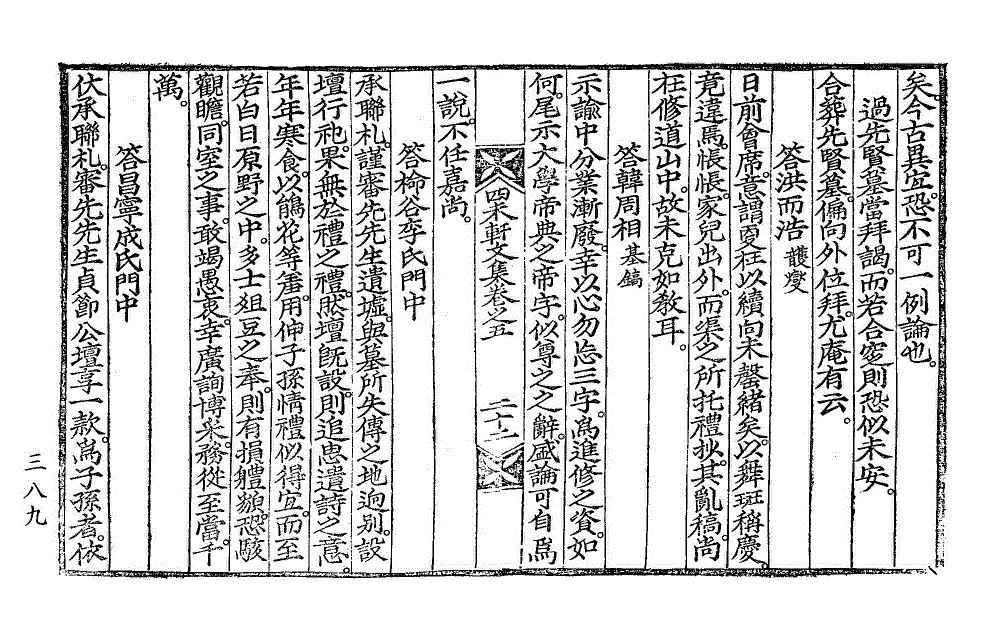 矣。今古异宜。恐不可一例论也。
矣。今古异宜。恐不可一例论也。过先贤墓当拜谒。而若合窆则恐似未安。
合葬先贤墓。偏向外位拜。尤庵有云。
答洪而浩(頀燮)
日前会席。意谓更枉以续向未罄绪矣。以舞斑称庆。竟违焉。怅怅。家儿出外。而渠之所托礼抄。其乱稿。尚在修道山中。故未克如教耳。
答韩周相(基镐)
示谕中分业渐废。幸以心勿忘三字。为进修之资。如何。尾示大学帝典之帝字。似尊之之辞。盛论可自为一说。不任嘉尚。
答椧谷李氏门中
承联札。谨审先先生遗墟。与墓所失传之地迥别。设坛行祀。果无于礼之礼。然坛既设。则追思遗诗之意。年年寒食。以鹃花等羞。用伸子孙情礼似得宜。而至若白日原野之中。多士俎豆之奉。则有损体貌。恐骇观瞻。同室之事。敢竭愚衷。幸广询博采。务从至当。千万。
答昌宁成氏门中
伏承联札。审先先生贞节公坛享一款。为子孙者。依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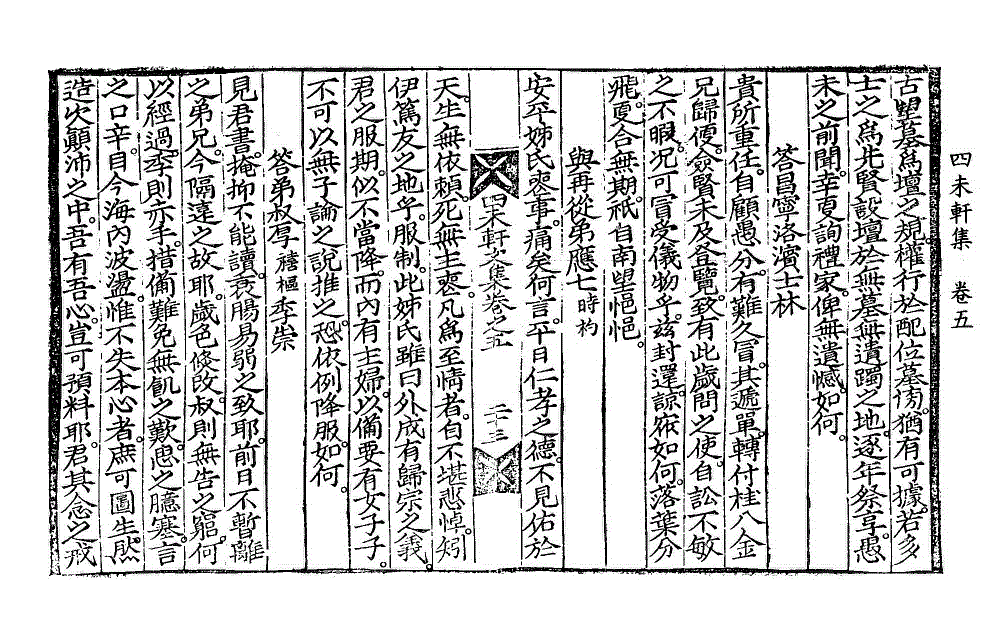 古望墓为坛之规。权行于配位墓傍。犹有可据。若多士之为先贤设坛于无墓无遗躅之地。逐年祭享。愚未之前闻。幸更询礼家。俾无遗憾。如何。
古望墓为坛之规。权行于配位墓傍。犹有可据。若多士之为先贤设坛于无墓无遗躅之地。逐年祭享。愚未之前闻。幸更询礼家。俾无遗憾。如何。答昌宁洛滨士林
贵所重任。自顾愚分。有难久冒。其递单。转付桂八金兄归便。佥贤未及登览。致有此岁问之使。自讼不敏之不暇。况可冒受仪物乎。玆封还。谅宱如何。落叶分飞。更合无期。祇自南望悒悒。
与再从弟应七(时杓)
安平姊氏丧事。痛矣何言。平日仁孝之德。不见佑于天。生无依赖。死无主丧。凡为至情者。自不堪悲悼。矧伊笃友之地乎。服制。此姊氏虽曰外成有归宗之义。君之服期。似不当降。而内有主妇。以备要有女子子。不可以无子论之说推之。恐依例降服。如何。
答弟叔厚(禧枢)季崇
见君书。掩抑不能读。衰肠易弱之致耶。前日不暂离之弟兄。今隔远之故耶。岁色倏改。叔则无告之穷。何以经过。季则赤手。措备难免无饥之叹。思之臆塞。言之口辛。目今海内波荡。惟不失本心者。庶可图生。然造次颠沛之中。吾有吾心。岂可预料耶。君其念之戒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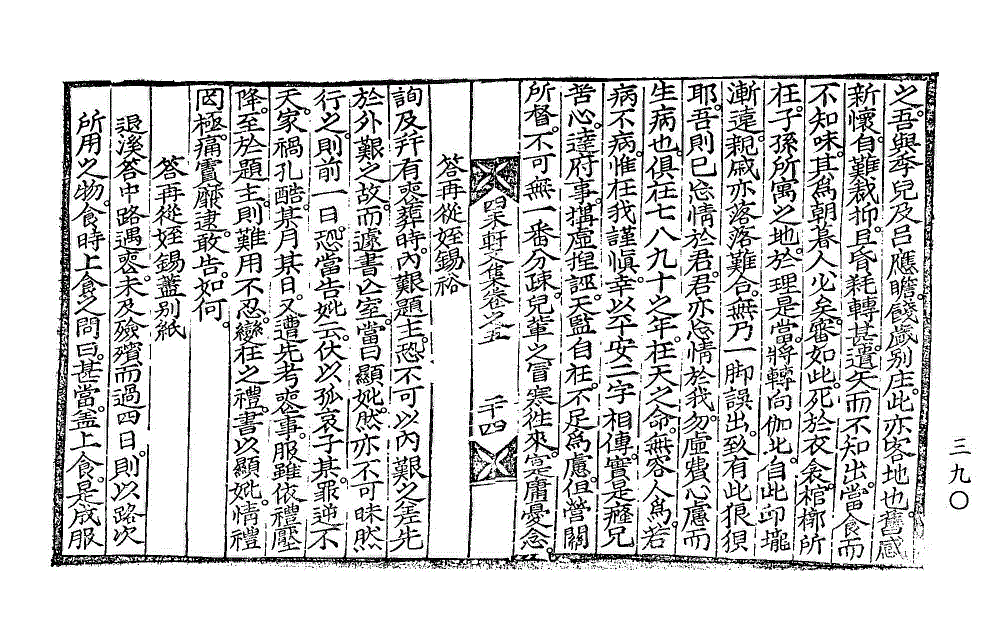 之。吾与季儿及吕应瞻。饯岁别庄。此亦客地也。旧感新怀。自难裁抑。且昏耗转甚。遗矢而不知出。当食而不知味。其为朝暮人必矣。审如此。死于衣衾。棺椁所在。子孙所寓之地。于理是当。将转向伽北。自此邱垄渐远。亲戚亦落落难合。无乃一脚误出。致有此狼狈耶。吾则已忘情于君。君亦忘情于我。勿虚费心虑而生病也。俱在七八九十之年。在天之命。无容人为。若病不病。惟在我谨慎。幸以平安二字相传。实是癃兄苦心。达府事。搆虚捏诬。天监自在。不足为虑。但营关所督。不可无一番分疏。儿辈之冒寒往来。寔庸忧念。
之。吾与季儿及吕应瞻。饯岁别庄。此亦客地也。旧感新怀。自难裁抑。且昏耗转甚。遗矢而不知出。当食而不知味。其为朝暮人必矣。审如此。死于衣衾。棺椁所在。子孙所寓之地。于理是当。将转向伽北。自此邱垄渐远。亲戚亦落落难合。无乃一脚误出。致有此狼狈耶。吾则已忘情于君。君亦忘情于我。勿虚费心虑而生病也。俱在七八九十之年。在天之命。无容人为。若病不病。惟在我谨慎。幸以平安二字相传。实是癃兄苦心。达府事。搆虚捏诬。天监自在。不足为虑。但营关所督。不可无一番分疏。儿辈之冒寒往来。寔庸忧念。答再从侄锡𥙿
询及并有丧葬时。内艰题主。恐不可以内艰之差先于外艰之故。而遽书亡室。当曰显妣。然亦不可昧然行之。则前一日。恐当告妣云。伏以孤哀子某。罪逆不天。家祸孔酷。某月某日。又遭先考丧事。服虽依礼压降。至于题主。则难用不忍。变在之礼。书以显妣。情礼罔极。痛霣靡逮。敢告。如何。
答再从侄锡荩别纸
退溪答中路遇丧。未及殓殡而过四日。则以路次所用之物。食时上食之问曰。甚当。盖上食。是成服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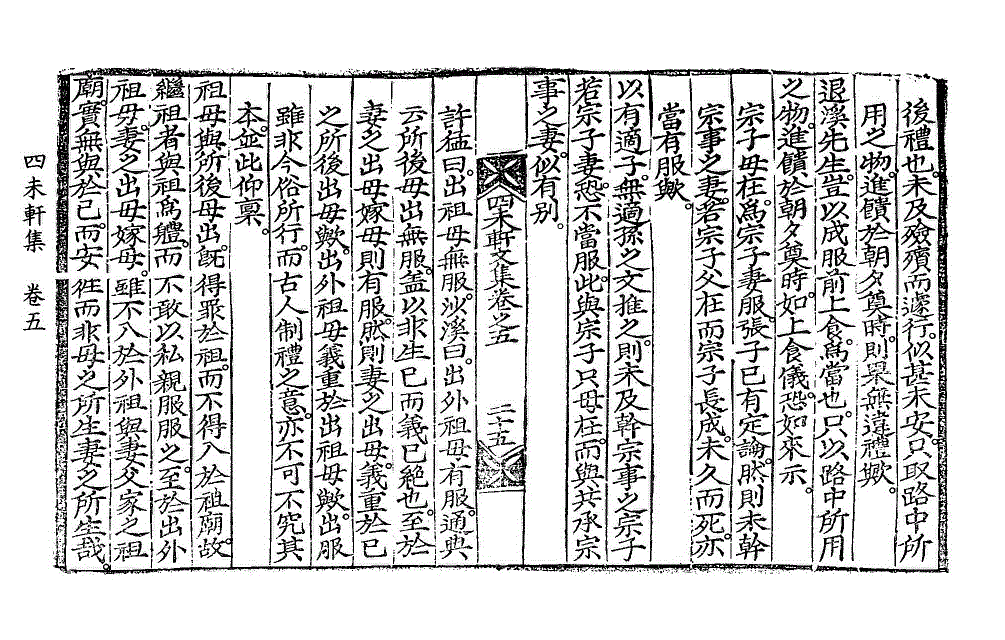 后礼也。未及殓殡而遽行。似甚未安。只取路中所用之物。进馈于朝夕奠时。则果无违礼欤。
后礼也。未及殓殡而遽行。似甚未安。只取路中所用之物。进馈于朝夕奠时。则果无违礼欤。退溪先生。岂以成服前上食。为当也。只以路中所用之物。进馈于朝夕奠时。如上食仪。恐如来示。
宗子母在。为宗子妻服。张子已有定论。然则未干宗事之妻。若宗子父在而宗子长成。未久而死。亦当有服欤。
以有适子。无适孙之文推之。则未及干宗事之宗子若宗子妻。恐不当服。此与宗子只母在。而与共承宗事之妻。似有别。
许猛曰。出祖母无服。沙溪曰。出外祖母有服。通典云所后母出无服。盖以非生己而义已绝也。至于妻之出母嫁母则有服。然则妻之出母。义重于己之所后出母欤。出外祖母义重于出祖母欤。出服虽非今俗所行。而古人制礼之意。亦不可不究其本。并此仰禀。
祖母与所后母出。既得罪于祖。而不得入于祖庙。故继祖者与祖为体。而不敢以私亲服服之。至于出外祖母。妻之出母嫁母。虽不入于外祖与妻父家之祖庙。实无与于己。而安往而非母之所生妻之所生哉。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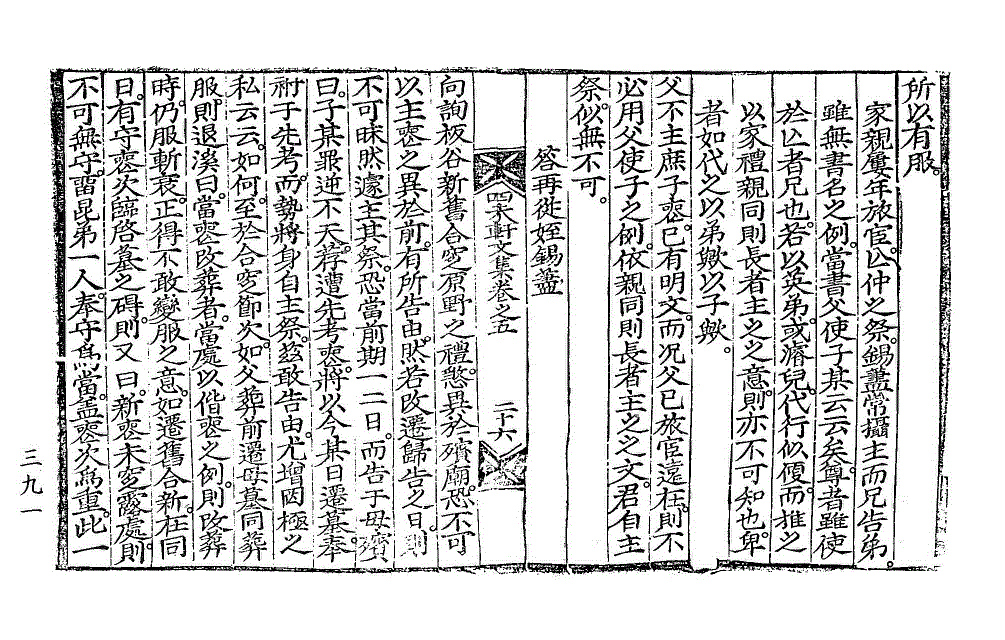 所以有服。
所以有服。家亲屡年旅宦。亡仲之祭。锡荩常摄主而兄告弟。虽无书名之例。当书父使子某云云矣。尊者虽使于亡者兄也。若以英弟。或浚儿。代行似便。而推之以家礼亲同则长者主之之意。则亦不可知也。卑者如代之以弟欤以子欤。
父不主庶子丧。已有明文。而况父已旅宦远在。则不必用父使子之例。依亲同则长者主之之文。君自主祭。似无不可。
答再从侄锡荩
向询板谷新旧合窆原野之礼。煞异于殡庙。恐不可以主丧之异于前。有所告由。然若改迁归告之日。则不可昧然遽主其祭。恐当前期一二日。而告于母殡曰。子某罪逆不天。荐遭先考丧。将以今某日迁墓。奉祔于先考。而势将身自主祭。玆敢告由。尤增罔极之私云云。如何。至于合窆节次。如父葬前迁母墓同葬服。则退溪曰。当丧改葬者。当处以偕丧之例。则改葬时。仍服斩衰。正得不敢变服之意。如迁旧合新。在同日。有守丧次临启墓之碍。则又曰。新丧未窆露处。则不可无守。留昆弟一人。奉守为当。盖丧次为重。此一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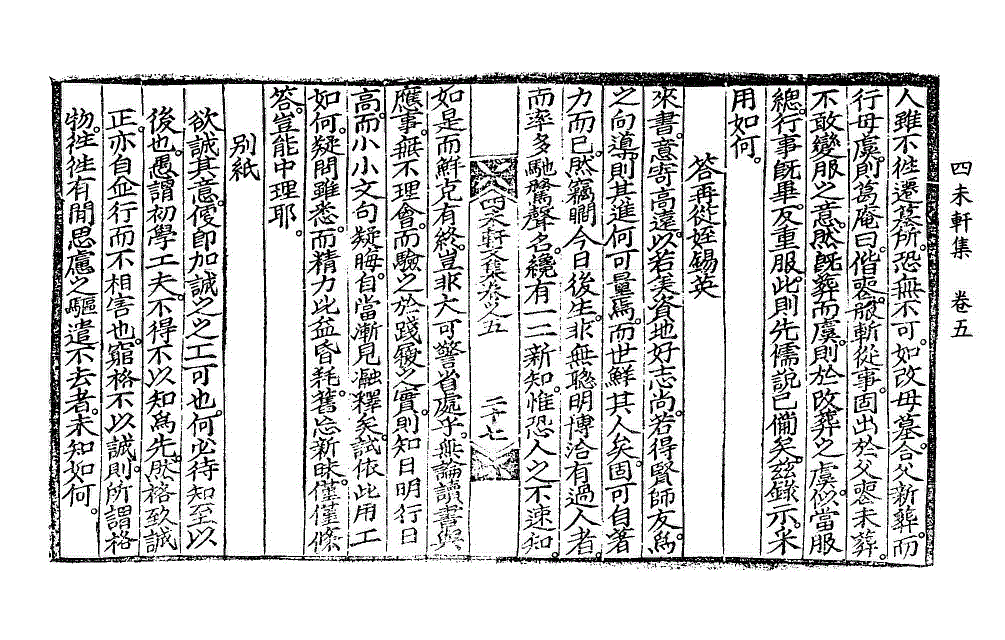 人虽不往迁墓所。恐无不可。如改母墓。合父新葬。而行母虞。则葛庵曰。偕丧。殷斩从事。固出于父丧未葬。不敢变服之意。然既葬而虞。则于改葬之虞。似当服缌。行事既毕。反重服。此则先儒说已备矣。玆录示。采用如何。
人虽不往迁墓所。恐无不可。如改母墓。合父新葬。而行母虞。则葛庵曰。偕丧。殷斩从事。固出于父丧未葬。不敢变服之意。然既葬而虞。则于改葬之虞。似当服缌。行事既毕。反重服。此则先儒说已备矣。玆录示。采用如何。答再从侄锡英
来书。意寄高远。以若美资地好志尚。若得贤师友。为之向导。则其进何可量焉。而世鲜其人矣。固可自著力而已。然窃瞷今日后生。非无聪明博洽有过人者。而率多驰骛声名。才有一二新知。惟恐人之不速知。如是而鲜克有终。岂非大可警省处乎。无论读书与应事。无不理会。而验之于践履之实。则知日明行日高。而小小文句疑晦。自当渐见瀜释矣。试依此用工如何。疑问虽悉。而精力比益昏耗。旧忘新昧。仅仅条答。岂能中理耶。
别纸
欲诚其意。便即加诚之之工可也。何必待知至以后也。愚谓初学工夫。不得不以知为先。然格致诚正。亦自并行而不相害也。穷格不以诚。则所谓格物。往往有间思虑之驱遣不去者。未知如何。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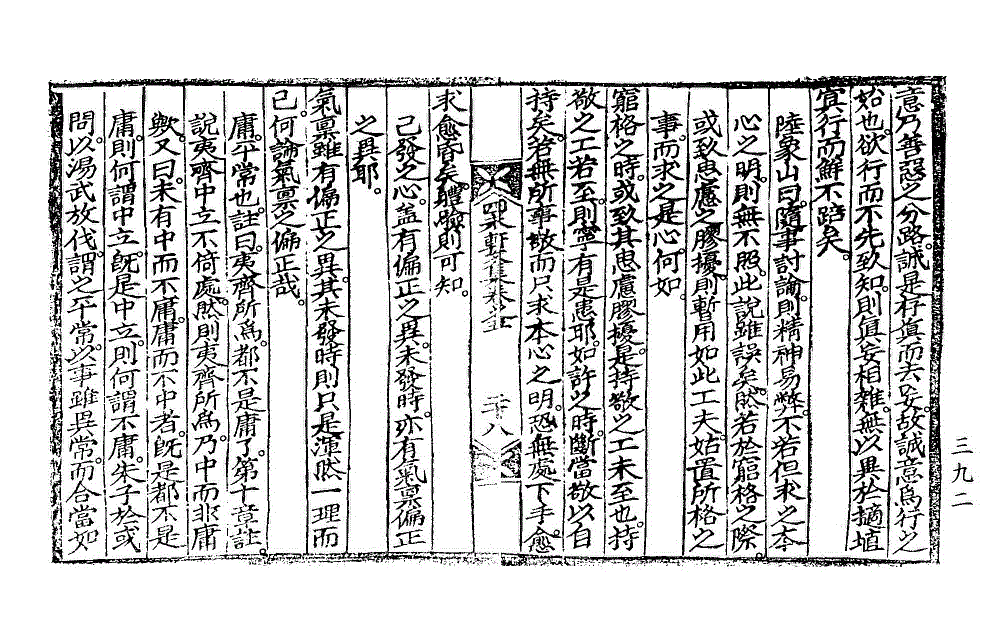 意乃善恶之分路。诚是存真而去妄。故诚意为行之始也。欲行而不先致知。则真妄相杂。无以异于擿埴冥行而鲜不踣矣。
意乃善恶之分路。诚是存真而去妄。故诚意为行之始也。欲行而不先致知。则真妄相杂。无以异于擿埴冥行而鲜不踣矣。陆象山曰。随事讨论。则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本心之明。则无不照。此说虽误矣。然若于穷格之际。或致思虑之胶扰。则暂用如此工夫。姑置所格之事。而求之是心。何如。
穷格之时。或致其思虑胶扰。是持敬之工未至也。持敬之工若至。则宁有是患耶。如许之时。断当敬以自持矣。若无所事敬而只求本心之明。恐无处下手。愈求愈昏矣。体脸则可知。
已发之心。盖有偏正之异。未发时。亦有气禀偏正之异耶。
气禀虽有偏正之异。其未发时则只是浑然一理而已。何论气禀之偏正哉。
庸。平常也。注曰。夷齐所为。都不是庸了。第十章注。说夷齐中立不倚处。然则夷齐所为。乃中而非庸欤。又曰。未有中而不庸。庸而不中者。既是都不是庸。则何谓中立。既是中立。则何谓不庸。朱子于或问。以汤武放伐。谓之平常。以事虽异常。而合当如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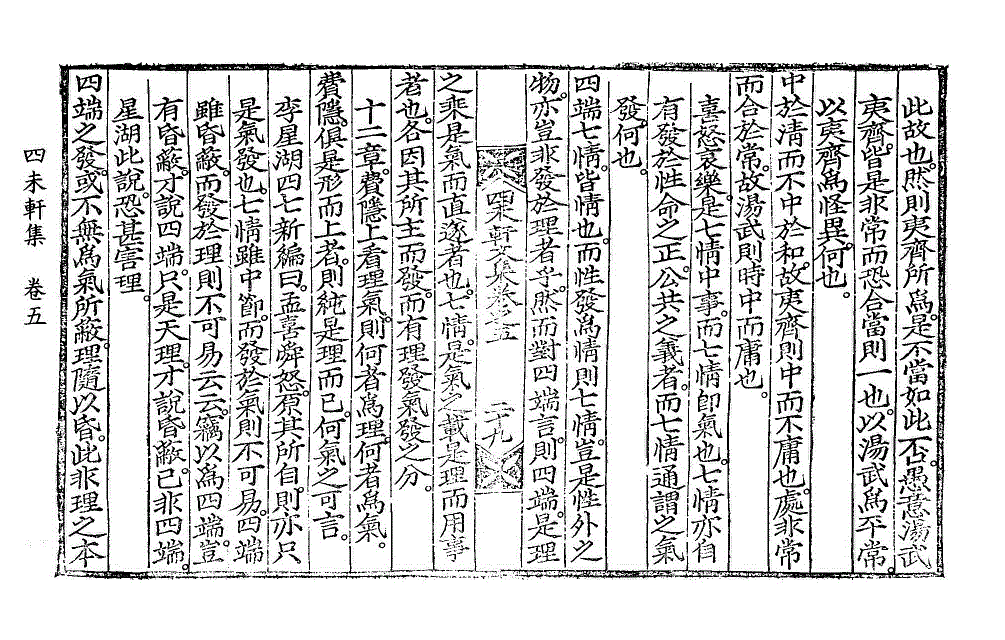 此故也。然则夷齐所为。是不当如此否。愚意汤武夷齐。皆是非常而恐合当则一也。以汤武为平常。以夷齐为怪异。何也。
此故也。然则夷齐所为。是不当如此否。愚意汤武夷齐。皆是非常而恐合当则一也。以汤武为平常。以夷齐为怪异。何也。中于清而不中于和。故夷齐则中而不庸也。处非常而合于常。故汤武则时中而庸也。
喜怒哀乐。是七情中事。而七情即气也。七情亦自有发于性命之正。公共之义者。而七情通谓之气发。何也。
四端七情。皆情也。而性发为情则七情。岂是性外之物。亦岂非发于理者乎。然而对四端言。则四端。是理之乘是气而直遂者也。七情。是气之载是理而用事者也。各因其所主而发。而有理发气发之分。
十二章。费隐上看理气。则何者为理。何者为气。
费隐。俱是形而上者。则纯是理而已。何气之可言。
李星湖四七新编曰。孟喜舜怒。原其所自。则亦只是气发也。七情虽中节。而发于气则不可易。四端虽昏蔽。而发于理则不可易云云。窃以为四端。岂有昏蔽。才说四端。只是天理。才说昏蔽。已非四端。星湖此说。恐甚害理。
四端之发。或不无为气所蔽。理随以昏。此非理之本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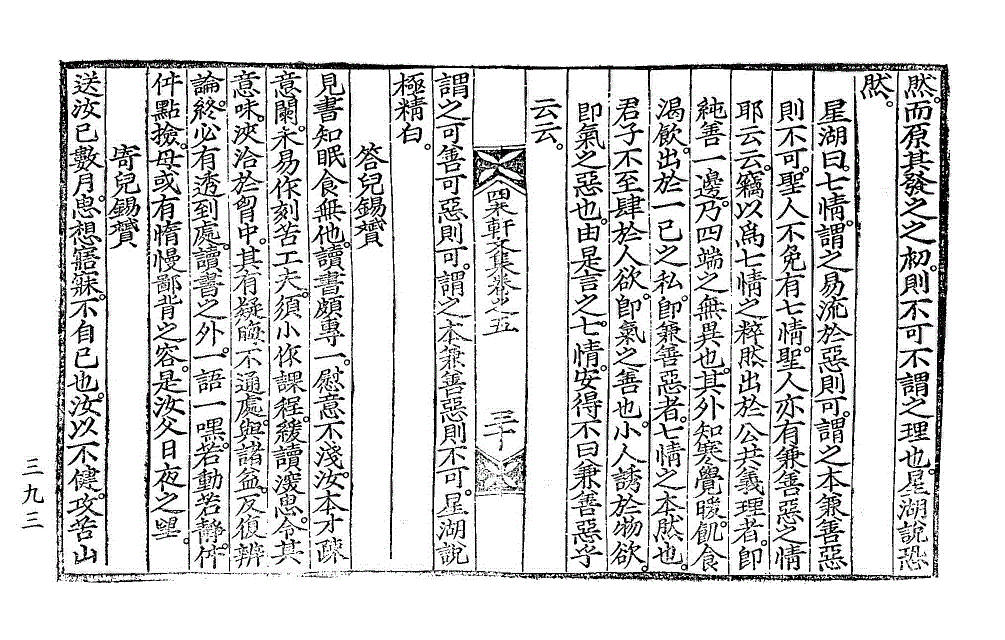 然。而原其发之之初。则不可不谓之理也。星湖说恐然。
然。而原其发之之初。则不可不谓之理也。星湖说恐然。星湖曰。七情。谓之易流于恶则可。谓之本兼善恶则不可。圣人不免有七情。圣人亦有兼善恶之情耶云云。窃以为七情之粹然出于公共义理者。即纯善一边。乃四端之无异也。其外知寒觉暖。饥食渴饮。出于一己之私。即兼善恶者。七情之本然也。君子不至肆于人欲。即气之善也。小人诱于物欲。即气之恶也。由是言之。七情。安得不曰兼善恶乎云云。
谓之可善可恶则可。谓之本兼善恶则不可。星湖说极精白。
答儿锡赟
见书知眠食无他。读书颇专一。慰意不浅。汝本才疏意阑。未易作刻苦工夫。须小作课程。缓读深思。令其意味。浃洽于胸中。其有疑晦不通处。与诸益。反复辨论。终必有透到处。读书之外。一语一嘿。若动若静。件件点捡。毋或有惰慢鄙背之容。是汝父日夜之望。
寄儿锡赟
送汝已数月。思想寤寐。不自已也。汝以不健。攻苦山
四未轩文集卷之五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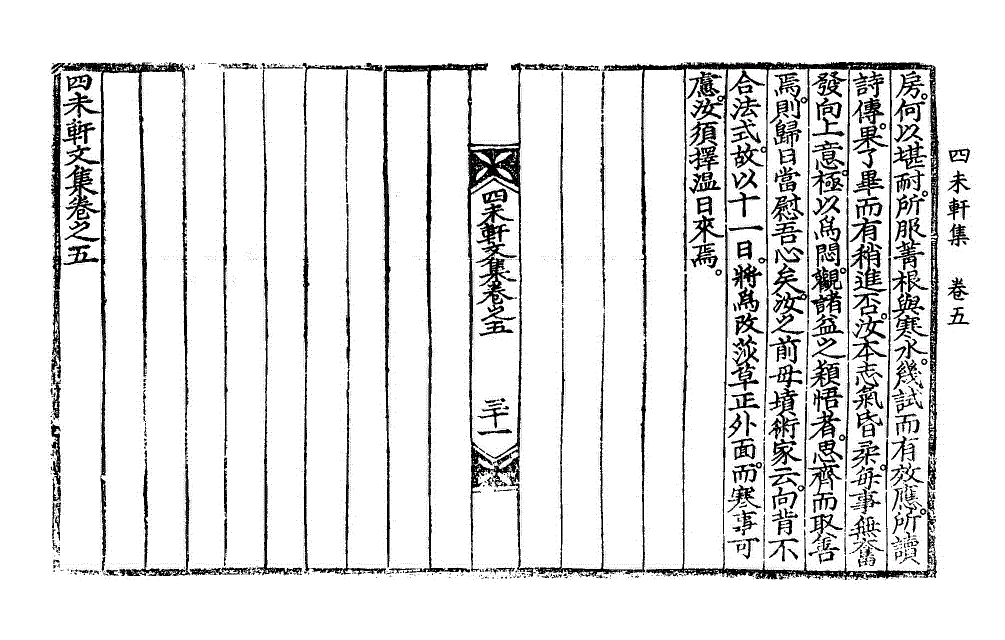 房。何以堪耐。所服菁根与寒水。几试而有效应。所读诗传。果了毕而有稍进否。汝本志气昏柔。每事无奋发向上意。极以为闷。观诸益之颖悟者。思齐而取善焉。则归日当慰吾心矣。汝之前母坟术家云。向背不合法式。故以十一日。将为改莎草正外面。而寒事可虑。汝须择温日来焉。
房。何以堪耐。所服菁根与寒水。几试而有效应。所读诗传。果了毕而有稍进否。汝本志气昏柔。每事无奋发向上意。极以为闷。观诸益之颖悟者。思齐而取善焉。则归日当慰吾心矣。汝之前母坟术家云。向背不合法式。故以十一日。将为改莎草正外面。而寒事可虑。汝须择温日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