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书(礼疑问答)
答姜参判(兰馨)
松岘再从叔(判书时永)成服才过。而侍生祖考忌日隔旬。虽将祀无碍耶。
礼外丧。自齐衰以下行也。注齐衰异门则祭。此谓吉祭也。忌日丧馀也。且殡后也异宫也。行之似可矣。而参酌减损。稍存不侑酳不酢之义。恐未知如何。
书(礼疑问答)
答姜参判(兰馨)
松岘再从叔(判书时永)成服才过。而侍生祖考忌日隔旬。虽将祀无碍耶。
礼外丧。自齐衰以下行也。注齐衰异门则祭。此谓吉祭也。忌日丧馀也。且殡后也异宫也。行之似可矣。而参酌减损。稍存不侑酳不酢之义。恐未知如何。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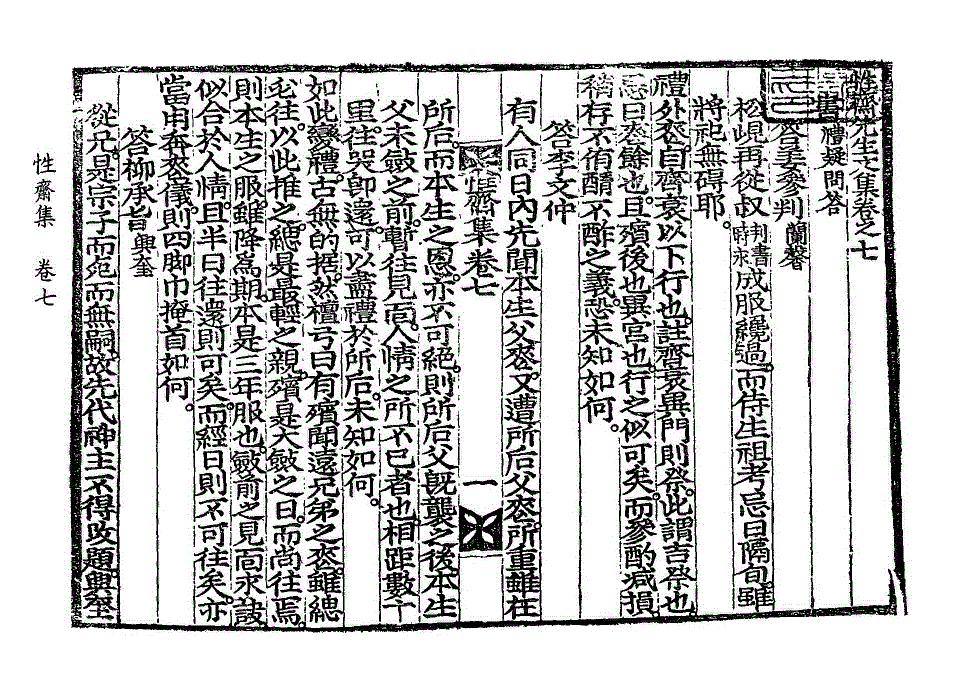 答李文仲
答李文仲有人同日内先闻本生父丧。又遭所后父丧。所重虽在所后。而本生之恩。亦不可绝。则所后父既袭之后。本生父未敛之前。暂往见面。人情之所不已者也。相距数十里。往哭即还。可以尽礼于所后。未知如何。
如此变礼。古无的据。然檀弓曰有殡闻远兄弟之丧。虽缌必往。以此推之。缌是最轻之亲。殡是大敛之日。而尚往焉。则本生之服。虽降为期。本是三年服也。敛前之见面永诀。似合于人情。且半日往还则可矣。而经日则不可往矣。亦当用奔丧仪。则四脚巾掩首如何。
答柳承旨(兴奎)
从兄。是宗子而死而无嗣。故先代神主不得改题。兴奎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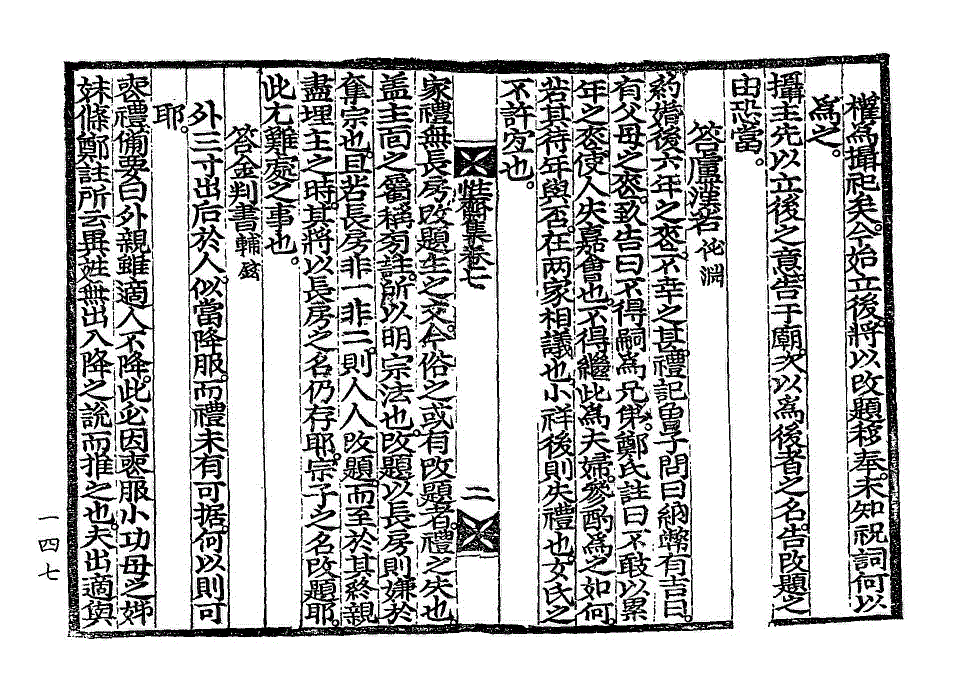 权为摄祀矣。今始立后。将以改题移奉。未知祝词何以为之。
权为摄祀矣。今始立后。将以改题移奉。未知祝词何以为之。摄主先以立后之意。告于庙。次以为后者之名。告改题之由恐当。
答卢汉若(佖渊)
约婚后六年之丧。不幸之甚。礼记曾子问曰纳币有吉日。有父母之丧。致告曰不得嗣为兄弟。郑氏注曰不敢以累年之丧。使人失嘉会也。不得继此为夫妇。参酌为之如何。若其待年与否。在两家相议也。小祥后则失礼也。女氏之不许宜也。
家礼无长房改题主之文。今俗之或有改题者。礼之失也。盖主面之属称旁注。所以明宗法也。改题以长房则嫌于夺宗也。且若长房非一非二。则人人改题。而至于其终亲尽埋主之时。其将以长房之名仍存耶。宗子之名改题耶。此尤难处之事也。
答金判书(辅铉)
外三寸出后于人。似当降服。而礼未有可据。何以则可耶。
丧礼备要曰外亲虽适人不降。此必因丧服小功母之姊妹条郑注所云异姓无出入降之说而推之也。夫出适与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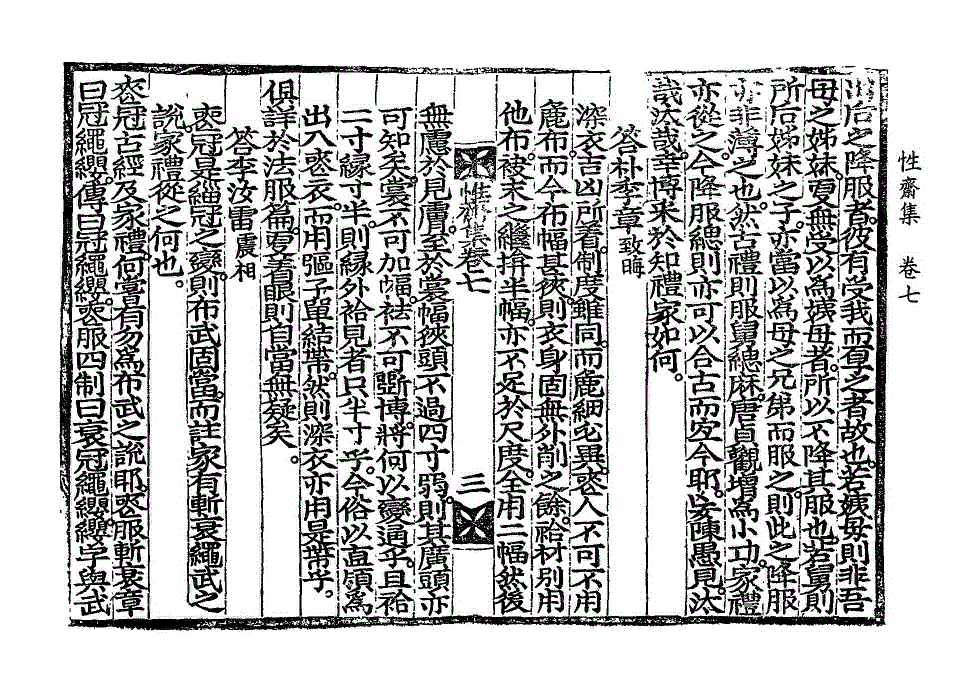 出后之降服者。彼有受我而厚之者故也。若姨母则非吾母之姊妹。更无受以为姨母者。所以不降其服也。若舅则所后姊妹之子。亦当以为母之兄弟而服之。则此之降服亦非薄之也。然古礼则服舅缌麻。唐贞观增为小功。家礼亦从之。今降服缌则亦可以合古而宜今耶。妄陈愚见。汰哉汰哉。幸博采于知礼家如何。
出后之降服者。彼有受我而厚之者故也。若姨母则非吾母之姊妹。更无受以为姨母者。所以不降其服也。若舅则所后姊妹之子。亦当以为母之兄弟而服之。则此之降服亦非薄之也。然古礼则服舅缌麻。唐贞观增为小功。家礼亦从之。今降服缌则亦可以合古而宜今耶。妄陈愚见。汰哉汰哉。幸博采于知礼家如何。答朴季章(致晦)
深衣吉凶所着。制度虽同。而粗细必异。丧人不可不用粗布。而今布幅甚狭。则衣身固无外削之馀。袷材别用他布。袂末之继掩半幅。亦不足于尺度。全用二幅然后无虑于见肤。至于裳幅狭头不过四寸弱。则其广头亦可知矣。裳不可加幅。袪不可斲博。将何以变通乎。且袷二寸缘寸半。则缘外袷见者只半寸乎。今俗以直领为出入丧衣。而用彄子单结带。然则深衣亦用是带乎。
俱详于法服篇。更着眼则自当无疑矣。
答李汝雷(震相)
丧冠是缁冠之变。则布武固当。而注家有斩衰绳武之说。家礼从之何也。
丧冠古经及家礼。何尝有勿为布武之说耶。丧服斩衰章曰冠绳缨。传曰冠绳缨。丧服四制曰衰冠绳缨。缨字与武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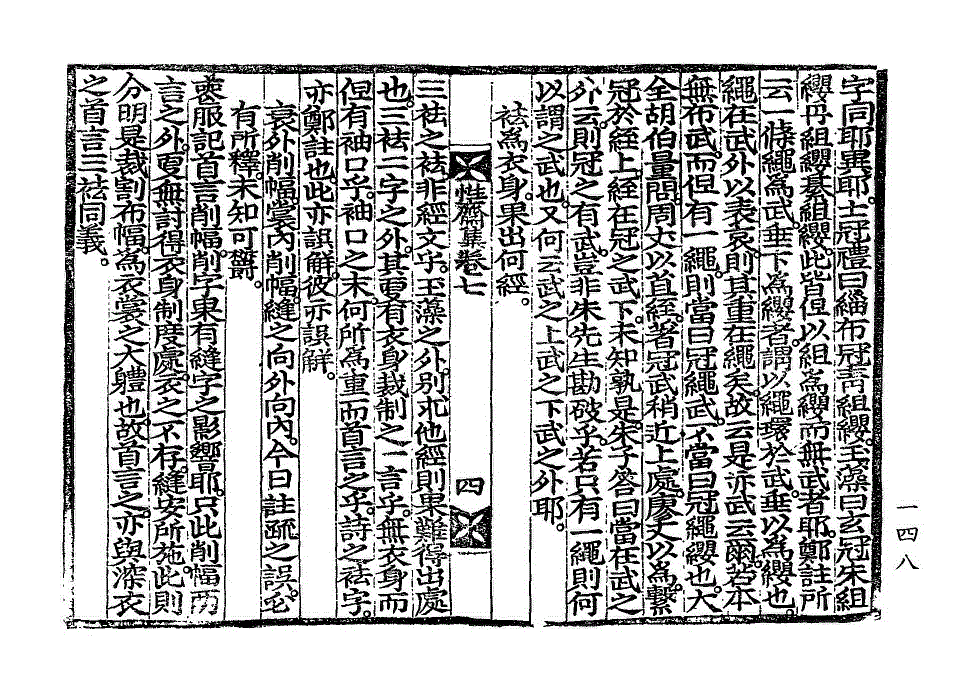 字同耶异耶。士冠礼曰缁布冠青组缨。玉藻曰玄冠朱组缨丹组缨綦组缨。此皆但以组为缨而无武者耶。郑注所云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者。谓以绳环于武。垂以为缨也。绳在武外以表哀。则其重在绳矣。故云是亦武云尔。若本无布武。而但有一绳。则当曰冠绳武。不当曰冠绳缨也。大全胡伯量问。周丈以苴绖。著冠武稍近上处。廖丈以为。系冠于绖上。绖在冠之武下。未知孰是。朱子答曰当在武之外云。则冠之有武。岂非朱先生勘破乎。若只有一绳则何以谓之武也。又何云武之上武之下武之外耶。
字同耶异耶。士冠礼曰缁布冠青组缨。玉藻曰玄冠朱组缨丹组缨綦组缨。此皆但以组为缨而无武者耶。郑注所云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者。谓以绳环于武。垂以为缨也。绳在武外以表哀。则其重在绳矣。故云是亦武云尔。若本无布武。而但有一绳。则当曰冠绳武。不当曰冠绳缨也。大全胡伯量问。周丈以苴绖。著冠武稍近上处。廖丈以为。系冠于绖上。绖在冠之武下。未知孰是。朱子答曰当在武之外云。则冠之有武。岂非朱先生勘破乎。若只有一绳则何以谓之武也。又何云武之上武之下武之外耶。袪为衣身。果出何经。
三袪之袪。非经文乎。玉藻之外。别求他经则果难得出处也。三袪二字之外。其更有衣身裁制之一言乎。无衣身而但有袖口乎。袖口之末。何所为重而首言之乎。诗之袪字。亦郑注也。此亦误解。彼亦误解。
衰外削幅。裳内削幅。缝之向外向内。今日注疏之误。必有所释。未知可郁。
丧服记首言削幅。削字果有缝字之影响耶。只此削幅两言之外。更无讨得衣身制度处。衣之不存。缝安所施。此则分明是裁割布幅。为衣裳之大体也。故首言之。亦与深衣之首言三袪同义。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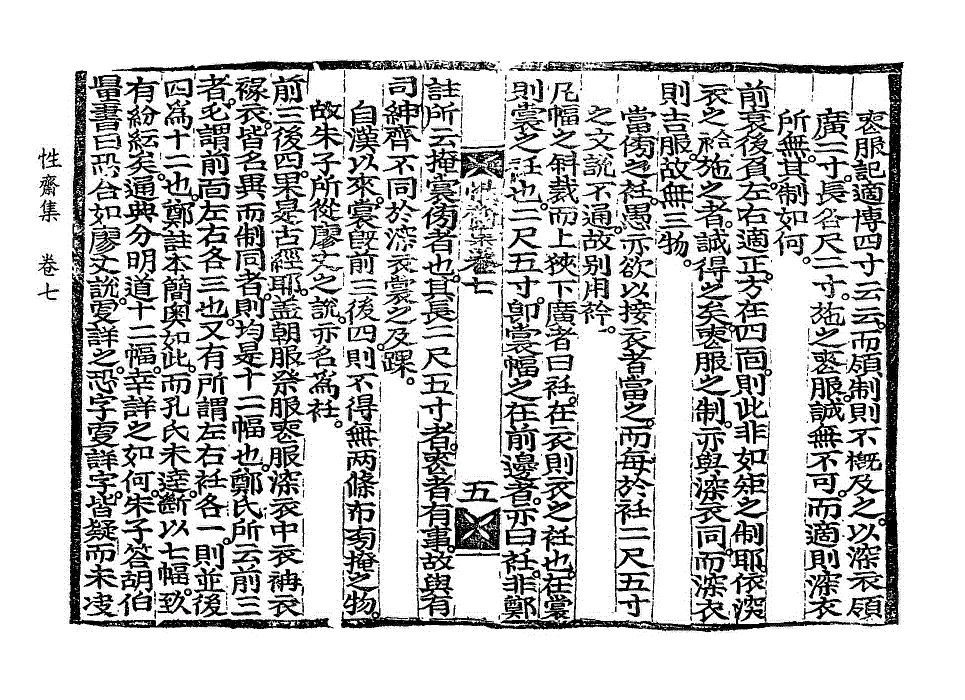 丧服记适博四寸云云。而领制则不概及之。以深衣领广二寸。长各尺二寸。施之丧服。诚无不可。而适则深衣所无。其制如何。
丧服记适博四寸云云。而领制则不概及之。以深衣领广二寸。长各尺二寸。施之丧服。诚无不可。而适则深衣所无。其制如何。前衰后负。左右适正。方在四面。则此非如矩之制耶。依深衣之袷施之者。诚得之矣。丧服之制。亦与深衣同。而深衣则吉服。故无三物。
当傍之衽。愚亦欲以接衣者当之。而每于衽二尺五寸之文说不通。故别用衿。
凡幅之斜裁而上狭下广者曰衽。在衣则衣之衽也。在裳则裳之衽也。二尺五寸。即裳幅之在前边者。亦曰衽。非郑注所云掩裳傍者也。其长二尺五寸者。丧者有事。故与有司绅齐不同于深衣裳之及踝。
自汉以来。裳既前三后四。则不得无两条布旁掩之物。故朱子所从廖丈之说。亦名为衽。
前三后四。果是古经耶。盖朝服祭服丧服深衣中衣袡衣褖衣。皆名异而制同者。则均是十二幅也。郑氏所云前三者。必谓前面左右各三也。又有所谓左右衽各一。则并后四为十二也。郑注本简奥如此。而孔氏未达。断以七幅。致有纷纭矣。通典分明道十二幅。幸详之如何。朱子答胡伯量书曰恐合如廖丈说。更详之。恐字更详字。皆疑而未决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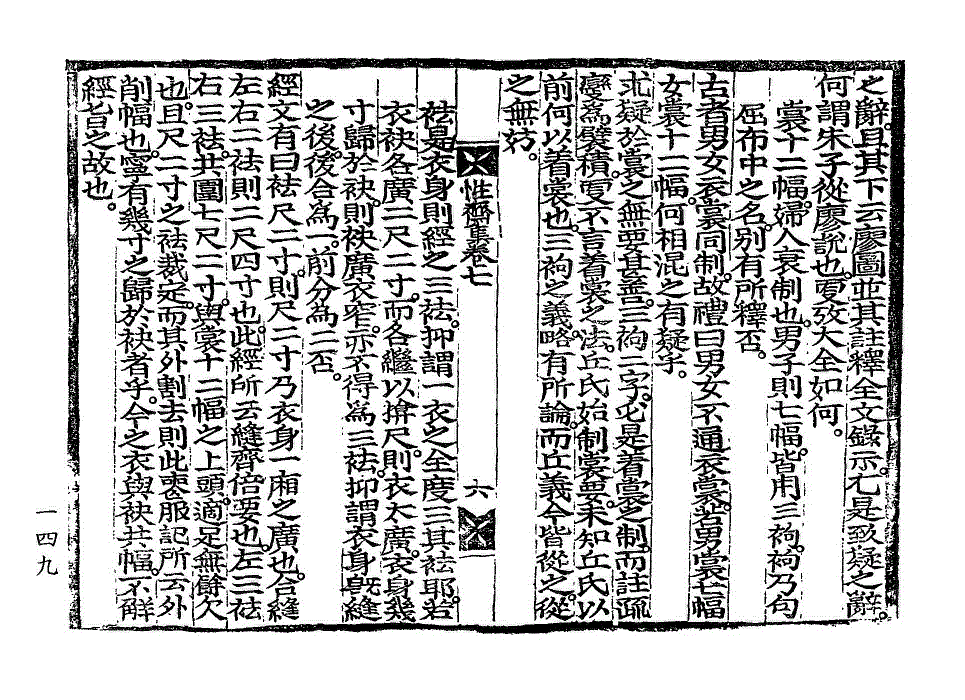 之辞。且其下云廖图并其注释全文录示。尤是致疑之辞。何谓朱子从廖说也。更考大全如何。
之辞。且其下云廖图并其注释全文录示。尤是致疑之辞。何谓朱子从廖说也。更考大全如何。裳十二幅。妇人衰制也。男子则七幅。皆用三袧。袧乃句屈布中之名。别有所释否。
古者男女衣裳同制。故礼曰男女不通衣裳。若男裳七幅女裳十二幅。何相混之有疑乎。
求疑于裳之无要甚善。三袧二字。必是着裳之制。而注疏变为襞积。更不言着裳之法。丘氏始制裳要。未知丘氏以前何以着裳也。三袧之义。略有所论。而丘义今皆从之。从之无妨。
袪是衣身则经之三袪。抑谓一衣之全度三其袪耶。若衣袂各广二尺二寸。而各继以掩尺。则衣太广。衣身几寸归于袂。则袂广衣窄。亦不得为三袪。抑谓衣身既缝之后。后合为一。前分为二否。
经文有曰袪尺二寸。则尺二寸乃衣身一厢之广也。合缝左右二袪则二尺四寸也。此经所云缝齐倍要也。左三袪右三袪。共围七尺二寸。与裳十二幅之上头。适足无馀欠也。且尺二寸之袪裁定。而其外割去则此丧服记所云外削幅也。宁有几寸之归于袂者乎。今之衣与袂共幅。不解经旨之故也。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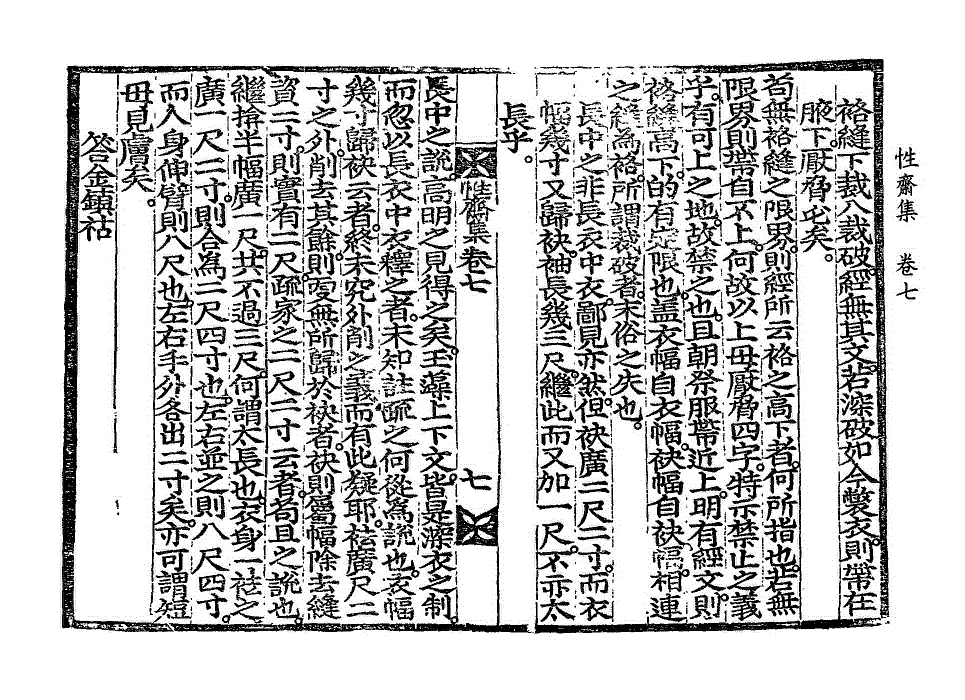 袼缝下裁入裁破。经无其文。若深破如今𧝟衣。则带在腋下。厌胁必矣。
袼缝下裁入裁破。经无其文。若深破如今𧝟衣。则带在腋下。厌胁必矣。苟无袼缝之限界。则经所云袼之高下者。何所指也。若无限界则带自不上。何故以上毋厌胁四字。特示禁止之义乎。有可上之地。故禁之也。且朝祭服带近上。明有经文。则袼缝高下。的有定限也。盖衣幅自衣幅。袂幅自袂幅。相连之缝为袼。所谓裁破者。末俗之失也。
长中之非长衣中衣。鄙见亦然。但袂广二尺二寸。而衣幅几寸又归袂。袖长几三尺。继此而又加一尺。不亦太长乎。
长中之说。高明之见得之矣。玉藻上下文。皆是深衣之制。而忽以长衣中衣释之者。未知注疏之何从为说也。衣幅几寸归袂云者。终未究外削之义而有此疑耶。袪广尺二寸之外。削去其馀。则更无所归于袂者。袂则属幅除去缝资二寸。则实有二尺。疏家之二尺二寸云者。苟且之说也。继掩半幅广一尺。共不过三尺。何谓太长也。衣身一袪之广一尺二寸。则合为二尺四寸也。左右并之则八尺四寸。而人身伸臂则八尺也。左右手外各出二寸矣。亦可谓短毋见肤矣。
答金镇祜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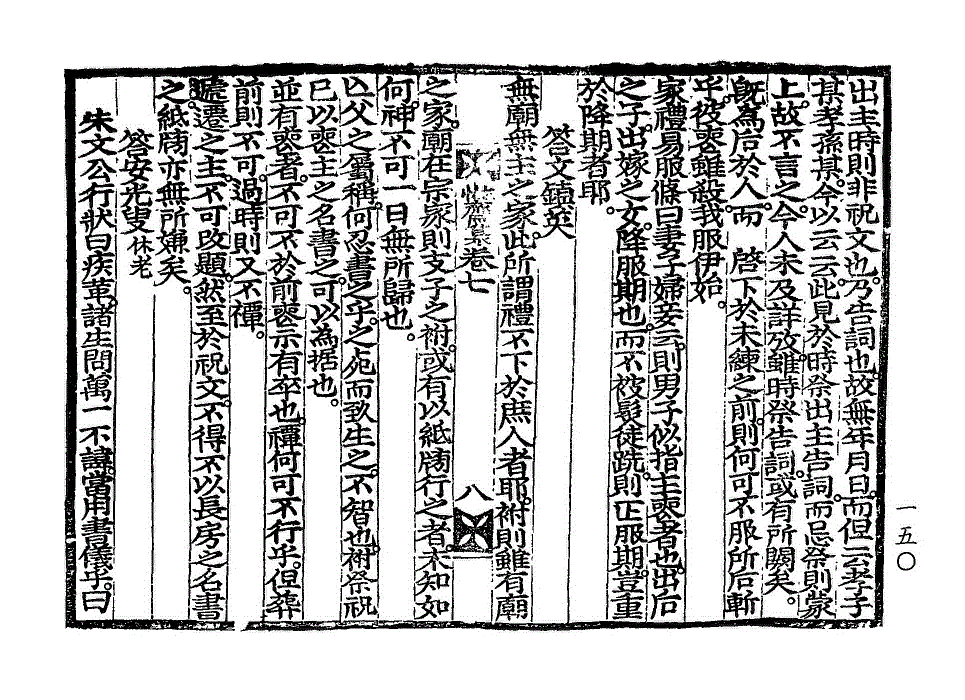 出主时则非祝文也。乃告词也。故无年月日。而但云孝子某孝孙某。今以云云。此见于时祭出主告词。而忌祭则蒙上。故不言之。今人未及详考。虽时祭告词。或有所阙矣。
出主时则非祝文也。乃告词也。故无年月日。而但云孝子某孝孙某。今以云云。此见于时祭出主告词。而忌祭则蒙上。故不言之。今人未及详考。虽时祭告词。或有所阙矣。既为后于人。而 启下于未练之前。则何可不服所后斩乎。彼丧虽杀。我服伊始。
家礼易服条曰妻子妇妾云。则男子似指主丧者也。出后之子。出嫁之女。降服期也。而不被发徒跣。则正服期。岂重于降期者耶。
答文镇英
无庙无主之家。此所谓礼不下于庶人者耶。祔则虽有庙之家。庙在宗家则支子之祔。或有以纸榜行之者。未知如何。神不可一日无所归也。
亡父之属称。何忍书之乎。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祔祭祝己以丧主之名书之。可以为据也。
并有丧者。不可不于前丧示有卒也。禫何可不行乎。但葬前则不可。过时则又不禫。
递迁之主。不可改题。然至于祝文。不得不以长房之名书之。纸榜亦无所嫌矣。
答安光叟(休老)
朱文公行状曰疾革。诸生问万一不讳。当用书仪乎。曰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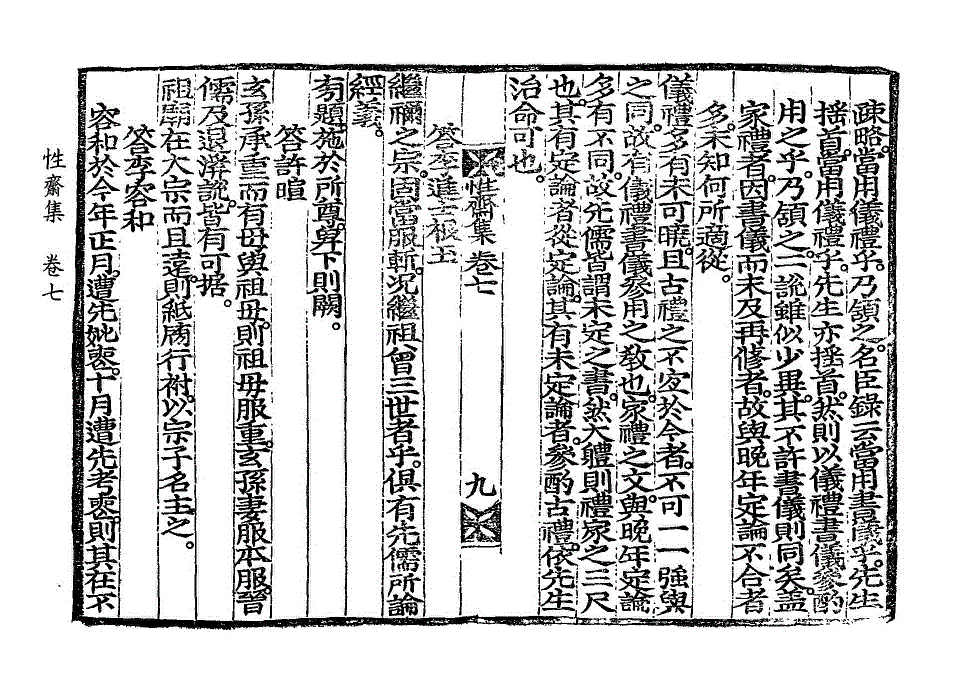 疏略。当用仪礼乎。乃颔之。名臣录云当用书仪乎。先生摇首。当用仪礼乎。先生亦摇首。然则以仪礼书仪参酌用之乎。乃颔之。二说虽似少异。其不许书仪则同矣。盖家礼者。因书仪而未及再修者。故与晚年定论不合者多。未知何所适从。
疏略。当用仪礼乎。乃颔之。名臣录云当用书仪乎。先生摇首。当用仪礼乎。先生亦摇首。然则以仪礼书仪参酌用之乎。乃颔之。二说虽似少异。其不许书仪则同矣。盖家礼者。因书仪而未及再修者。故与晚年定论不合者多。未知何所适从。仪礼多有未可晓。且古礼之不宜于今者。不可一一强与之同。故有仪礼书仪参用之教也。家礼之文。与晚年定论多有不同。故先儒皆谓未定之书。然大体则礼家之三尺也。其有定论者从定论。其有未定论者。参酌古礼。依先生治命可也。
答李进士(根玉)
继祢之宗。固当服斩。况继祖曾三世者乎。俱有先儒所论经义。
旁题。施于所尊。卑下则阙。
答许暄
玄孙承重而有母与祖母。则祖母服重。玄孙妻服本服。晋儒及退溪说。皆有可据。
祖庙在大宗而且远。则纸榜行祔。以宗子名主之。
答李容和
容和于今年正月。遭先妣丧。十月遭先考丧。则其在不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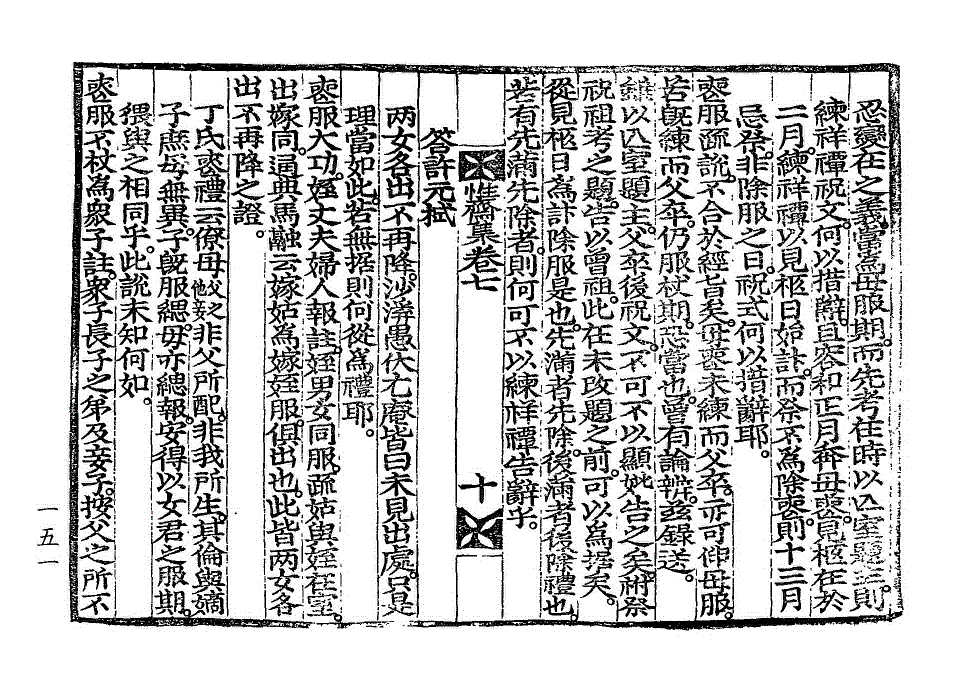 忍变在之义。当为母服期。而先考在时以亡室题主。则练祥禫祝文。何以措辞。且容和正月奔母丧。见柩在于二月。练祥禫以见柩日始计。而祭不为除丧。则十三月忌祭。非除服之日。祝式何以措辞耶。
忍变在之义。当为母服期。而先考在时以亡室题主。则练祥禫祝文。何以措辞。且容和正月奔母丧。见柩在于二月。练祥禫以见柩日始计。而祭不为除丧。则十三月忌祭。非除服之日。祝式何以措辞耶。丧服疏说。不合于经旨矣。母丧未练而父卒。亦可伸母服。若既练而父卒。仍服杖期。恐当也。曾有论辨。玆录送。
虽以亡室题主。父卒后祝文。不可不以显妣告之矣。祔祭祝祖考之题。告以曾祖。此在未改题之前。可以为据矣。
从见柩日为计除服是也。先满者先除。后满者后除礼也。若有先满先除者。则何可不以练祥禫告辞乎。
答许元栻
两女各出不再降。沙溪愚伏尤庵皆曰未见出处。只是理当如此。若无据则何从为礼耶。
丧服大功。侄丈夫妇人报注。侄男女同服。疏姑与侄在室。出嫁同。通典马融云嫁姑为嫁侄服。俱出也。此皆两女各出不再降之證。
丁氏丧礼云僚母(父之他妾)非父所配。非我所生。其伦与嫡子庶母无异。子既服缌。母亦缌报。安得以女君之服期。猥与之相同乎。此说未知何如。
丧服不杖为众子注。众子长子之弟及妾子。按父之所不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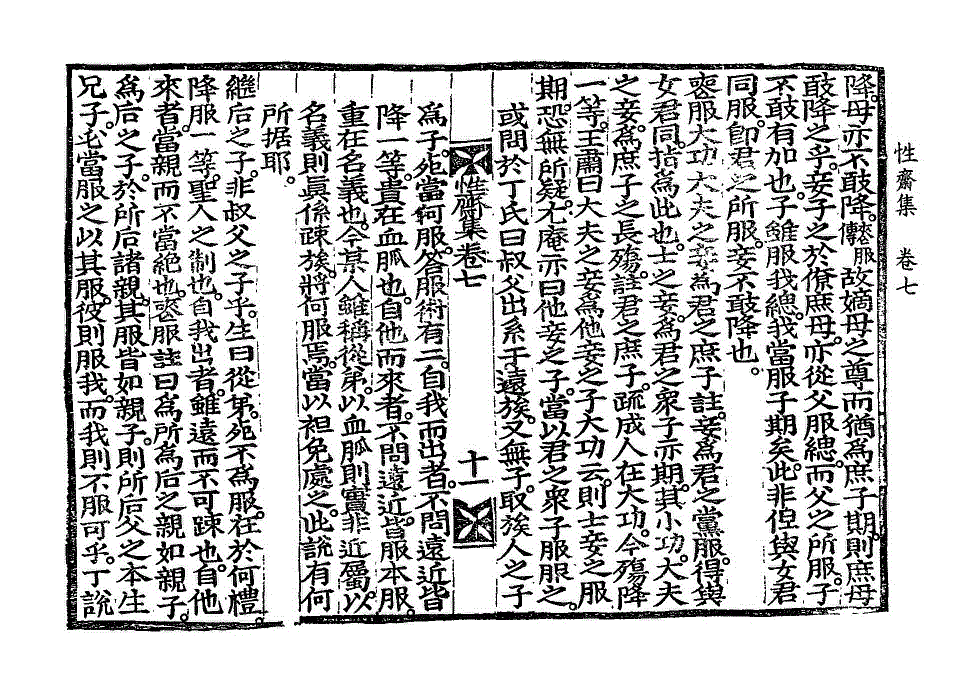 降。母亦不敢降。(丧服传)故嫡母之尊而犹为庶子期。则庶母敢降之乎。妾子之于僚庶母。亦从父服缌。而父之所服。子不敢有加也。子虽服我缌。我当服子期矣。此非但与女君同服。即君之所服。妾不敢降也。
降。母亦不敢降。(丧服传)故嫡母之尊而犹为庶子期。则庶母敢降之乎。妾子之于僚庶母。亦从父服缌。而父之所服。子不敢有加也。子虽服我缌。我当服子期矣。此非但与女君同服。即君之所服。妾不敢降也。丧服大功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注。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指为此也。士之妾。为君之众子亦期。其小功。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注君之庶子。疏成人在大功。今殇降一等。王肃曰大夫之妾为他妾之子大功云。则士妾之服期。恐无所疑。尤庵亦曰他妾之子。当以君之众子服服之。
或问于丁氏曰叔父出系于远族。又无子。取族人之子为子。死当何服。答服术有二。自我而出者。不问远近皆降一等。贵在血脉也。自他而来者。不问远近。皆服本服。重在名义也。今某人虽称从弟。以血脉则实非近属。以名义则真系疏族。将何服焉。当以袒免处之。此说有何所据耶。
继后之子。非叔父之子乎。生曰从弟。死不为服。在于何礼。降服一等。圣人之制也。自我出者。虽远而不可疏也。自他来者。当亲而不当绝也。丧服注曰为所为后之亲如亲子。为后之子。于所后诸亲。其服皆如亲子。则所后父之本生兄子。必当服之以其服。彼则服我。而我则不服可乎。丁说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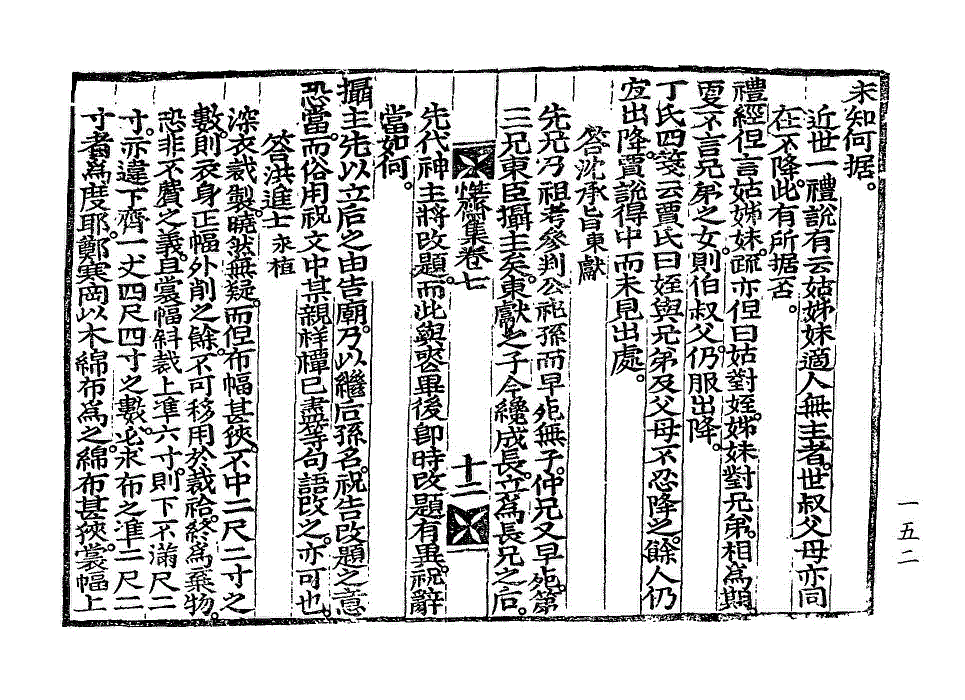 未知何据。
未知何据。近世一礼说有云姑姊妹适人无主者。世叔父母亦同在不降。此有所据否。
礼经但言姑姊妹。疏亦但曰姑对侄。姊妹对兄弟。相为期。更不言兄弟之女。则伯叔父。仍服出降。
丁氏四笺云贾氏曰侄与兄弟及父母不忍降之。馀人仍宜出降。贾说得中而未见出处。
答沈承旨(东献)
先兄乃祖考参判公祀孙而早死无子。仲兄又早死。第三兄东臣摄主矣。东献之子今才成长。立为长兄之后。先代神主将改题。而此与丧毕后即时改题有异。祝辞当如何。
摄主先以立后之由告庙。乃以继后孙名。祝告改题之意恐当。而俗用祝文中某亲祥禫已尽等句语改之。亦可也。
答洪进士(永植)
深衣裁制。晓然无疑。而但布幅甚狭。不中二尺二寸之数。则衣身正幅外削之馀。不可移用于裁袷。终为弃物。恐非不费之义。且裳幅斜裁上准六寸。则下不满尺二寸。亦违下齐一丈四尺四寸之数。必求布之准二尺二寸者为度耶。郑寒冈以木绵布为之。绵布甚狭。裳幅上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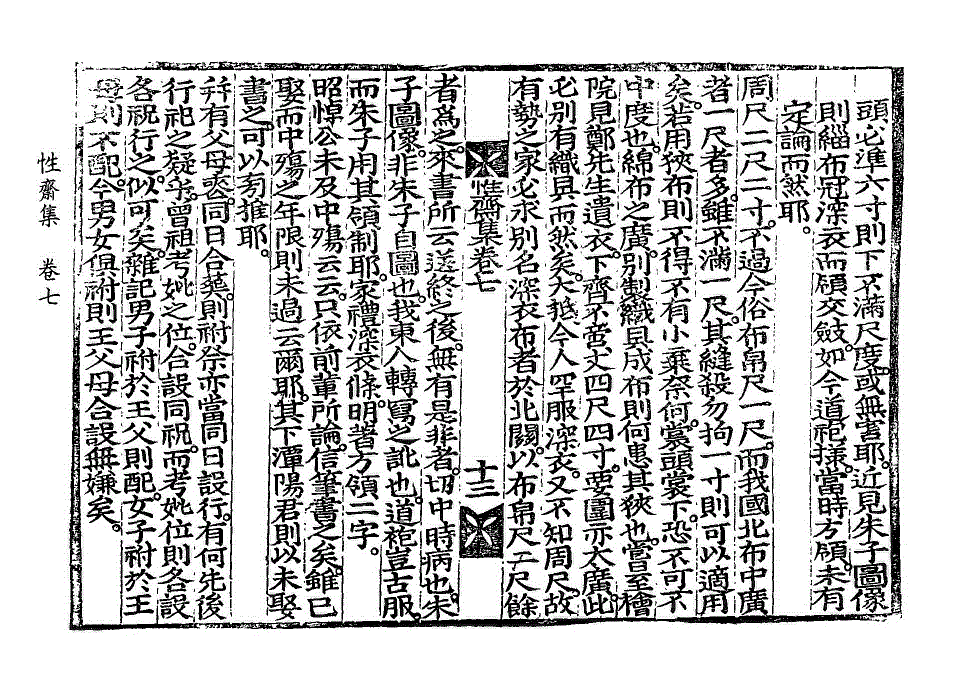 头必准六寸则下不满尺度。或无害耶。近见朱子图像则缁布冠深衣而领交敛。如今道袍㨾。当时方领。未有定论而然耶。
头必准六寸则下不满尺度。或无害耶。近见朱子图像则缁布冠深衣而领交敛。如今道袍㨾。当时方领。未有定论而然耶。周尺二尺二寸。不过今俗布帛尺一尺。而我国北布中广者一尺者多。虽不满一尺。其缝杀勿拘一寸则可以适用矣。若用狭布则不得不有小弃奈何。裳头裳下。恐不可不中度也。绵布之广。别制织具成布则何患其狭也。尝至桧院见郑先生遗衣。下齐不啻丈四尺四寸。要围亦太广。此必别有织具而然矣。大抵今人罕服深衣。又不知周尺。故有势之家必求别名深衣布者于北关。以布帛尺二尺馀者为之。来书所云送终之后。无有是非者。切中时病也。朱子图像。非朱子自图也。我东人转写之讹也。道袍岂古服。而朱子用其领制耶。家礼深衣条。明著方领二字。
昭悼公未及中殇云云。只依前辈所论。信笔书之矣。虽已娶而中殇之年限则未过云尔耶。其下潭阳君则以未娶书之。可以旁推耶。
并有父母丧。同日合葬。则祔祭亦当同日设行。有何先后行祀之疑乎。曾祖考妣之位。合设同祝。而考妣位则各设各祝行之。似可矣。杂记男子祔于王父则配。女子祔于王母则不配。今男女俱祔则王父母合设无嫌矣。
答郑承旨(谦植)
先妣小祥隔日。而子女以痘疫一时俱没。练祭似当退行。而人言不一。何以则可耶。
丧服传曰有死于宫中者则三月不举祭。杂记曰父母之丧将祭。而昆弟死。殡而祭。如同宫则虽臣妾葬而后祭。今子女之丧虽殇死。非臣妾之比。况二殇并在一室乎。星湖先生曰丧柩即去。祭不待三月。殇者已葬则即用今月下旬丁日。未知如何。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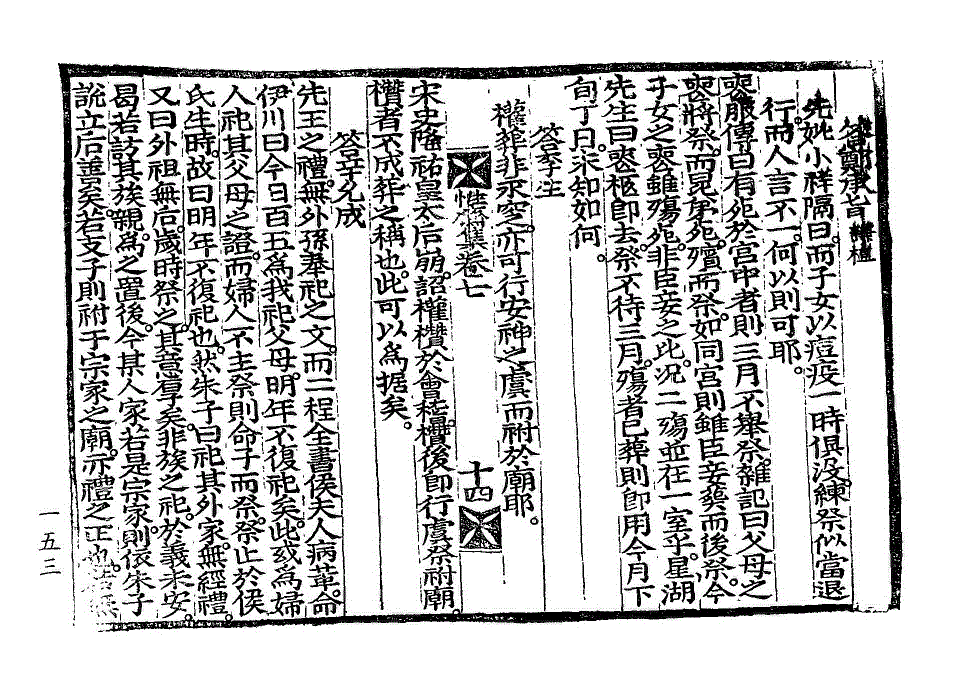 答李生
答李生权葬非永窆。亦可行安神之虞而祔于庙耶。
宋史隆祐皇太后崩。诏权攒于会稽。攒后即行虞祭祔庙。攒者不成葬之称也。此可以为据矣。
答辛允成
先王之礼。无外孙奉祀之文。而二程全书侯夫人病革。命伊川曰今日百五为我祀父母。明年不复祀矣。此或为妇人祀其父母之證。而妇人不主祭则命子而祭。祭止于侯氏生时。故曰明年不复祀也。然朱子曰祀其外家。无经礼。又曰外祖无后。岁时祭之。其意厚矣。非族之祀。于义未安。曷若访其族亲。为之置后。今某人家若是宗家。则依朱子说立后善矣。若支子则祔于宗家之庙。亦礼之正也。若无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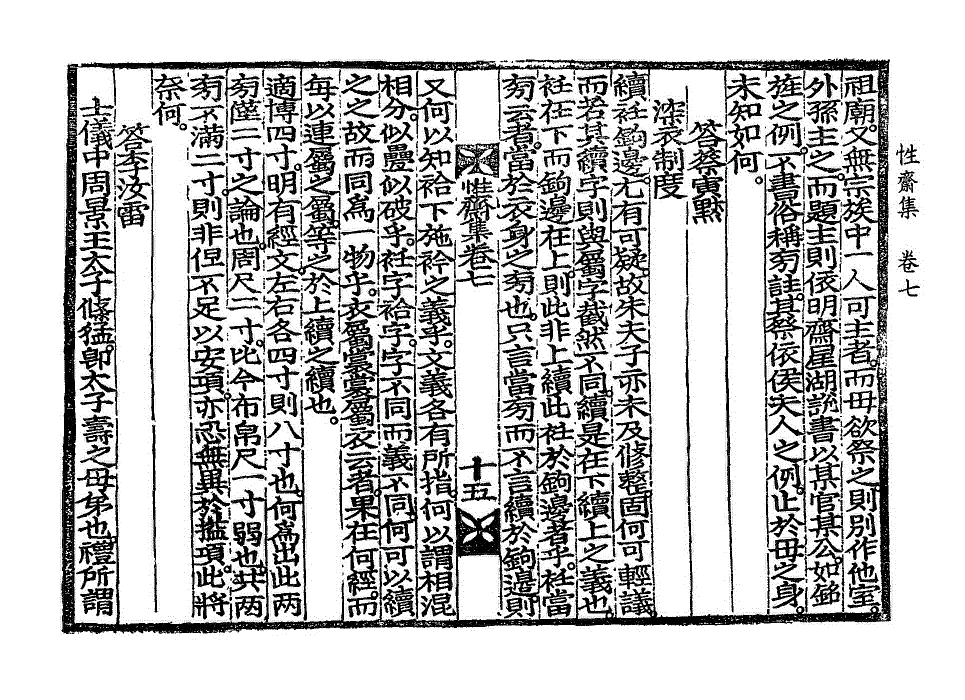 祖庙。又无宗族中一人可主者。而母欲祭之。则别作他室。外孙主之。而题主则依明斋星湖说书以某官某公。如铭旌之例。不书俗称旁注。其祭依侯夫人之例。止于母之身。未知如何。
祖庙。又无宗族中一人可主者。而母欲祭之。则别作他室。外孙主之。而题主则依明斋星湖说书以某官某公。如铭旌之例。不书俗称旁注。其祭依侯夫人之例。止于母之身。未知如何。答蔡寅默
深衣制度
续衽钩边。尤有可疑。故朱夫子亦未及修整。固何可轻议。而若其续字则与属字截然不同。续是在下续上之义也。衽在下而钩边在上。则此非上续此衽于钩边者乎。衽当旁云者。当于衣身之旁也。只言当旁而不言续于钩边。则又何以知袷下施衿之义乎。文义各有所指。何以谓相混相分。似叠似破乎。衽字袷字。字不同而义不同。何可以续之之故而同为一物乎。衣属裳裳属衣云者。果在何经。而每以连属之属。等之于上续之续也。
适博四寸。明有经文。左右各四寸则八寸也。何为出此两旁仅二寸之论也。周尺二寸。比今布帛尺一寸弱也。共两旁不满二寸。则非但不足以安项。亦恐无异于扼项。此将奈何。
答李汝雷
士仪中周景王太子条猛。即太子寿之母弟也。礼所谓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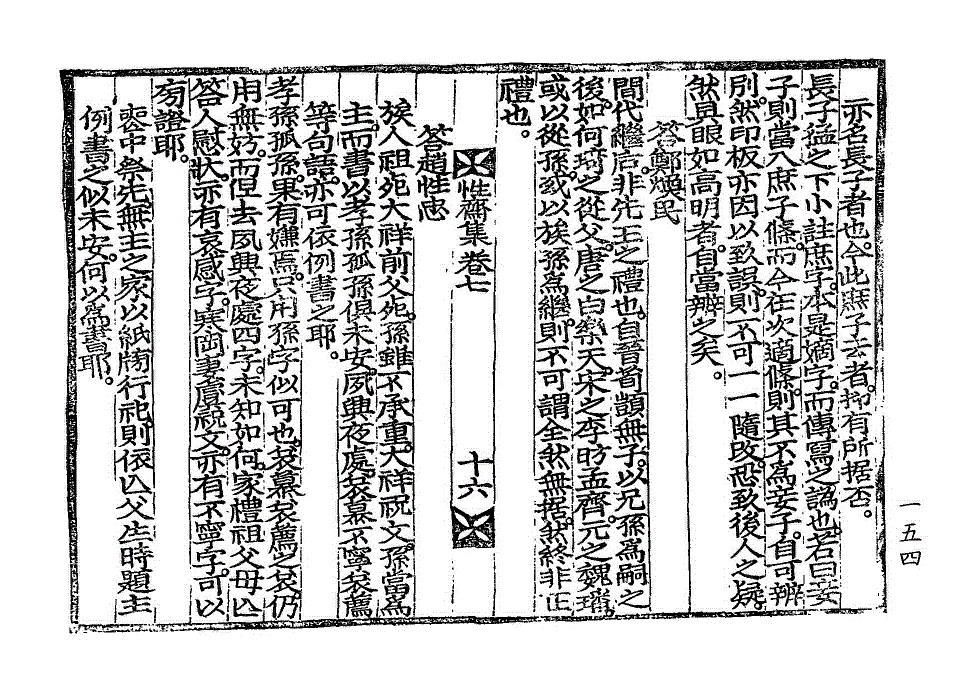 亦名长子者也。今此庶子云者。抑有所据否。
亦名长子者也。今此庶子云者。抑有所据否。长子猛之下小注庶字。本是嫡字。而传写之讹也。若曰妾子则当入庶子条。而今在次适条。则其不为妾子。自可辨别。然印板亦因以致误。则不可一一随改。恐致后人之疑。然具眼如高明者。自当辨之矣。
答郑焕民
间代继后。非先王之礼也。自晋荀顗无子。以兄孙为嗣之后。如何琦之从父。唐之白乐天。宋之李昉孟齐。元之魏璠。或以从孙。或以族孙为继。则不可谓全然无据。然终非正礼也。
答赵性忠
族人祖死大祥前父死。孙虽不承重。大祥祝文。孙当为主。而书以孝孙孤孙俱未安。夙兴夜处。哀慕不宁哀荐等句语。亦可依例书之耶。
孝孙孤孙。果有嫌焉。只用孙字似可也。哀慕哀荐之哀。仍用无妨。而但去夙兴夜处四字。未知如何。家礼祖父母亡答人慰状。亦有哀感字。寒冈妻虞祝文。亦有不宁字。可以旁證耶。
丧中祭先。无主之家以纸榜行祀。则依亡父生时题主例书之似未安。何以为书耶。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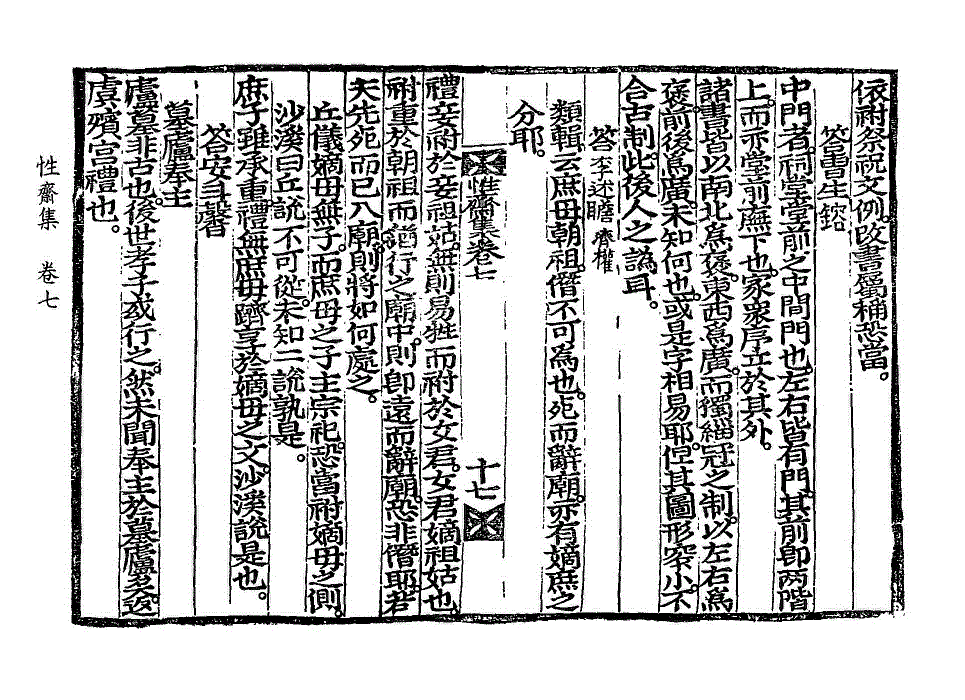 依祔祭祝文例。改书属称恐当。
依祔祭祝文例。改书属称恐当。答曹生镕
中门者。祠堂堂前之中间门也。左右皆有门。其前即两阶上。而亦堂前庑下也。家众序立于其外。
诸书皆以南北为褒。东西为广。而独缁冠之制。以左右为褒。前后为广。未知何也。或是字相易耶。但其图形窄小。不合古制。此后人之讹耳。
答李述瞻(济权)
类辑云庶母朝祖。僭不可为也。死而辞庙。亦有嫡庶之分耶。
礼妾祔于妾祖姑。无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女君嫡祖姑也。祔重于朝祖而犹行之庙中。则即远而辞庙。恐非僭耶。若夫先死而已入庙。则将如何处之。
丘仪嫡母无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恐当祔嫡母之侧。沙溪曰丘说不可从。未知二说孰是。
庶子虽承重。礼无庶母跻享于嫡母之文。沙溪说是也。
答安斗馨
墓庐奉主
庐墓非古也。后世孝子或行之。然未闻奉主于墓庐矣。返虞殡宫礼也。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5L 页
 杖
杖杖者所以扶病。非为祭时用也。若不得已有事出入时。杖而行可也。
绞带
绞带者。丧服之带也。丧服则首绖腰绖绞带具焉。出入时不着丧服。则独着绞带何义也。深衣则布带也。
礼无绞带三重四股之文。惟要绖练后易葛三重耳。
答赵玟奎
为人后者称其本生父母。古礼则但云其父母。(仪礼丧服)而宋人始称伯叔父母。此虽与古不同。然必是为后于父之兄弟。故曰伯父叔父也。非疏远之也。若出后于袒免以外之宗。则泛然以远族之称称之耶。
计出后亲疏而服之之说。刱于崔凯。非古礼也。礼有本生之文。称以本生父母本生兄弟。则无此弊。
丧期之三月五月九月期年三年。必用阳数何哉。阳有生意。抑孝子不忍死其亲。而为致生之义耶。
三月一时也。五月二时也。七月(殇大功)九月三时也。期年四时也。至于三年则加隆也。以亲之远近。制服之轻重也。阴阳死生之说。未知何据也。
答文郁纯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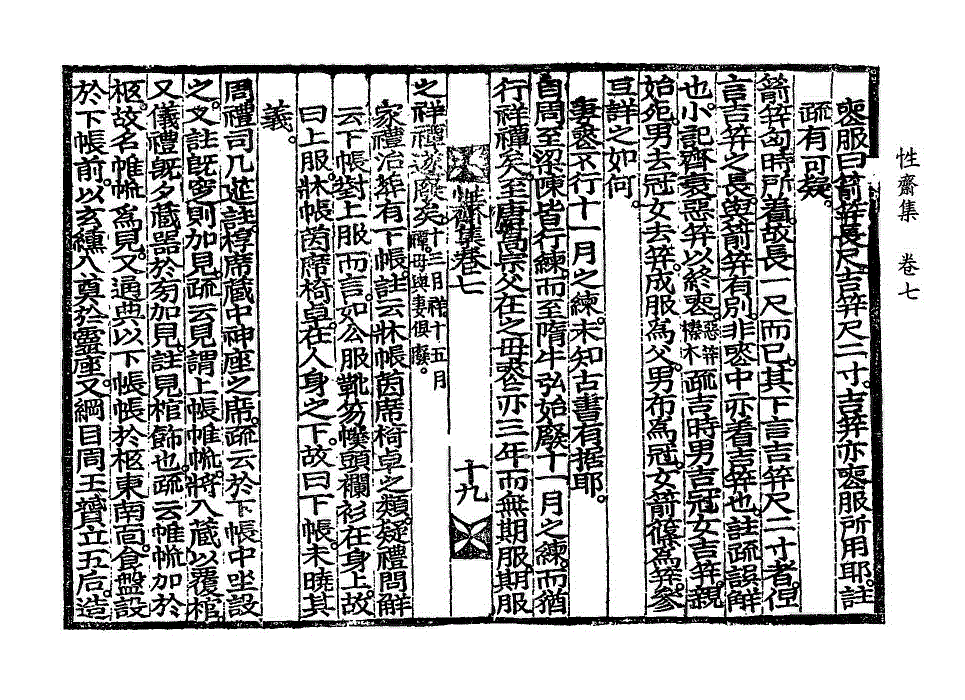 丧服曰箭笄长尺。吉笄尺二寸。吉笄亦丧服所用耶。注疏有可疑。
丧服曰箭笄长尺。吉笄尺二寸。吉笄亦丧服所用耶。注疏有可疑。箭笄匈时所着。故长一尺而已。其下言吉笄尺二寸者。但言吉笄之长。与箭笄有别。非丧中亦着吉笄也。注疏误解也。小记齐衰恶笄以终丧。(恶笄榛木)疏吉时男吉冠女吉笄。亲始死。男去冠女去笄。成服为父。男布为冠。女箭筱为笄。参互详之如何。
妻丧不行十一月之练。未知古书有据耶。
自周至梁陈皆行练。而至隋牛弘始废十一月之练。而犹行祥禫矣。至唐高宗父在之母丧亦三年而无期服。期服之祥禫遂废矣。(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母与妻俱废。)
家礼治葬有下帐。注云床帐茵席椅卓之类。疑礼问解云下帐对上服而言。如公服靴笏,幞头襕衫在身上。故曰上服。床帐茵席椅卓。在人身之下。故曰下帐。未晓其义。
周礼司几筵注。椁席藏中神座之席。疏云于下帐中坐设之。又注既窆则加见。疏云见谓上帐帷㡆。将入藏以覆棺。又仪礼既夕藏器于旁加见。注见棺饰也。疏云帷㡆加于柩。故名帷㡆为见。又通典以下帐帐于柩东南面。食盘设于下帐前。以玄纁入奠于灵座。又纲目周王赟立五后。造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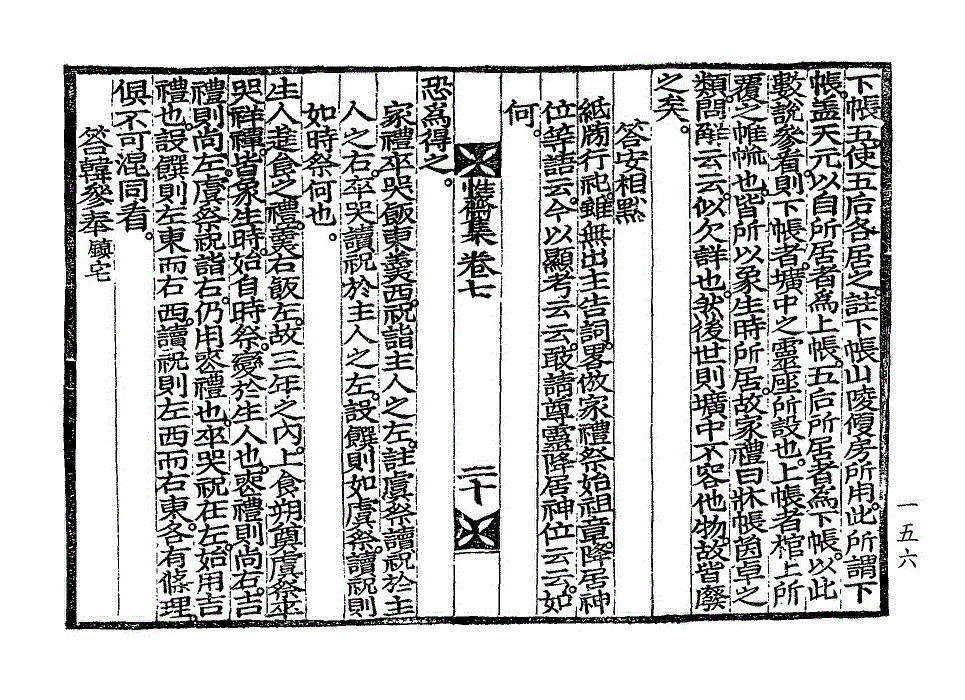 下帐五。使五后各居之。注下帐山陵便房所用。此所谓下帐。盖天元以自所居者为上帐。五后所居者为下帐。以此数说参看。则下帐者。圹中之灵座所设也。上帐者棺上所覆之帷㡆也。皆所以象生时所居。故家礼曰床帐茵卓之类。问解云云。似欠详也。然后世则圹中不容他物。故皆废之矣。
下帐五。使五后各居之。注下帐山陵便房所用。此所谓下帐。盖天元以自所居者为上帐。五后所居者为下帐。以此数说参看。则下帐者。圹中之灵座所设也。上帐者棺上所覆之帷㡆也。皆所以象生时所居。故家礼曰床帐茵卓之类。问解云云。似欠详也。然后世则圹中不容他物。故皆废之矣。答安相默
纸榜行祀。虽无出主告词。略仿家礼祭始祖章。降居神位等语云。今以显考云云。敢请尊灵降居神位云云。如何。
恐为得之。
家礼卒哭饭东羹西。祝诣主人之左。注虞祭读祝于主人之右。卒哭读祝于主人之左。设馔则如虞祭。读祝则如时祭何也。
生人进食之礼。羹右饭左。故三年之内。上食朔奠虞祭卒哭祥禫。皆象生时。始自时祭。变于生人也。丧礼则尚右。吉礼则尚左。虞祭祝诣右。仍用丧礼也。卒哭祝在左。始用吉礼也。设馔则左东而右西。读祝则左西而右东。各有条理。俱不可混同看。
答韩参奉(镇宅)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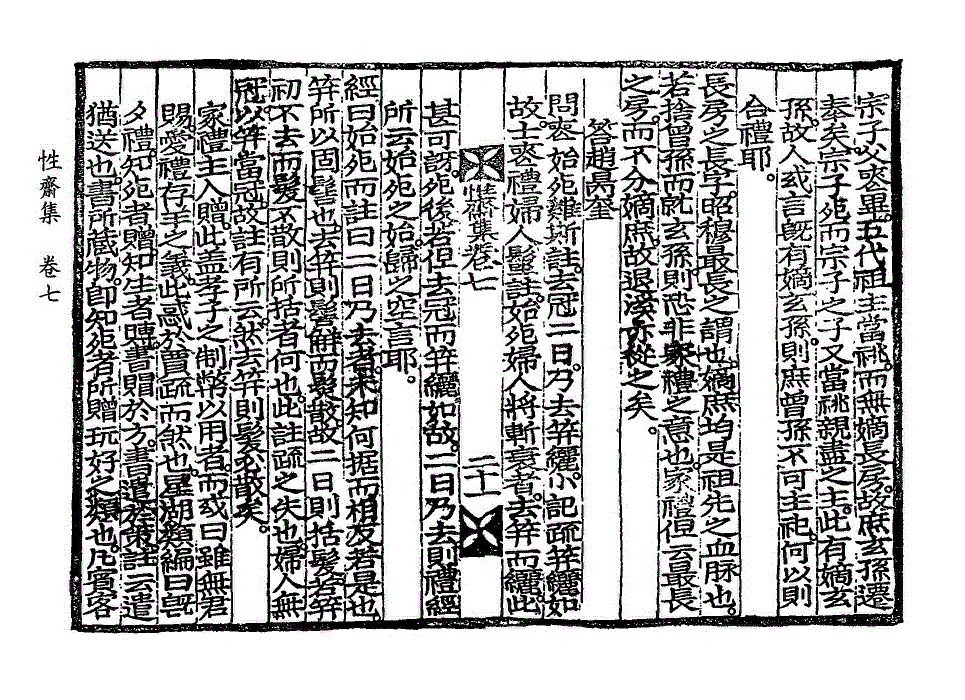 宗子父丧毕。五代祖主当祧。而无嫡长房。故庶玄孙迁奉矣。宗子死而宗子之子又当祧亲尽之主。此有嫡玄孙。故人或言既有嫡玄孙。则庶曾孙不可主祀。何以则合礼耶。
宗子父丧毕。五代祖主当祧。而无嫡长房。故庶玄孙迁奉矣。宗子死而宗子之子又当祧亲尽之主。此有嫡玄孙。故人或言既有嫡玄孙。则庶曾孙不可主祀。何以则合礼耶。长房之长字。昭穆最长之谓也。嫡庶均是祖先之血脉也。若舍曾孙而就玄孙。则恐非家礼之意也。家礼但云最长之房。而不分嫡庶。故退溪亦从之矣。
答赵炳奎
问丧始死鸡斯注。去冠二日。乃去笄纚。小记疏笄纚如故。士丧礼妇人髽注。始死妇人将斩衰者。去笄而纚。此甚可讶。死后若但去冠而笄纚如故。二日乃去。则礼经所云始死之始。归之空言耶。
经曰始死而注曰二日乃去者。未知何据而相反若是也。笄所以固髻也。去笄则髻解而发散。故二日则括发。若笄初不去而发不散则所括者何也。此注疏之失也。妇人无冠。以笄当冠。故注有所云。然去笄则发必散矣。
家礼主入赠。此盖孝子之制币以用者。而或曰虽无君赐。爱礼存羊之义。此惑于贾疏而然也。星湖类编曰既夕礼。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赗于方。书遣于策。注云遣犹送也。书所藏物。即知死者所赠玩好之类也。凡宾客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7L 页
 兄弟之赠。皆当书策而藏之。何独于君赠者为然乎。窆时主人袭。赠用制币。玄纁束稽颡。贾氏以此为君之前所赠也。若然君之所已赠。只可藏之而已。何必更言主人赠也。只当因其所赐而已。又何必更言制币也。哀亲之去。礼宜有币。有币则虽君赠之荣。不可因以为礼也。星湖之论。岂不明白耶。
兄弟之赠。皆当书策而藏之。何独于君赠者为然乎。窆时主人袭。赠用制币。玄纁束稽颡。贾氏以此为君之前所赠也。若然君之所已赠。只可藏之而已。何必更言主人赠也。只当因其所赐而已。又何必更言制币也。哀亲之去。礼宜有币。有币则虽君赠之荣。不可因以为礼也。星湖之论。岂不明白耶。愚亦有疑于此。尝以为虽无君赠。主人自当有币。略有所论辨。然始信贾疏而以既夕礼之主人赠。为君赐之币。檀弓之主人赠。为孝子之币矣。及见类编然后。乃知星湖之辨析。允得礼意也。
答吴敏泳
叔父没于去十二月。叔母没于今正月。从弟疑于所服。问于尹丈最植。则以贺循所云父死未殡而祖死。服祖以周。既殡而祖死。服祖三年之说及庾蔚之所云父亡未葬而祖死。不敢服祖重。不忍变在之说。参互为證。以为父丧未葬而遭母丧者。当依父在之例云。未知如何。
齐衰三年。父卒则为母。仪礼之文也。父卒后为祖父服斩。亦丧服记之文也。何必舍礼经。而拘于后儒短丧之论乎。且父丧中母服。父丧中祖服。各自不同。母则厌屈与不厌屈有别。祖则承重与不承重有别。何可混之乎。愚见则服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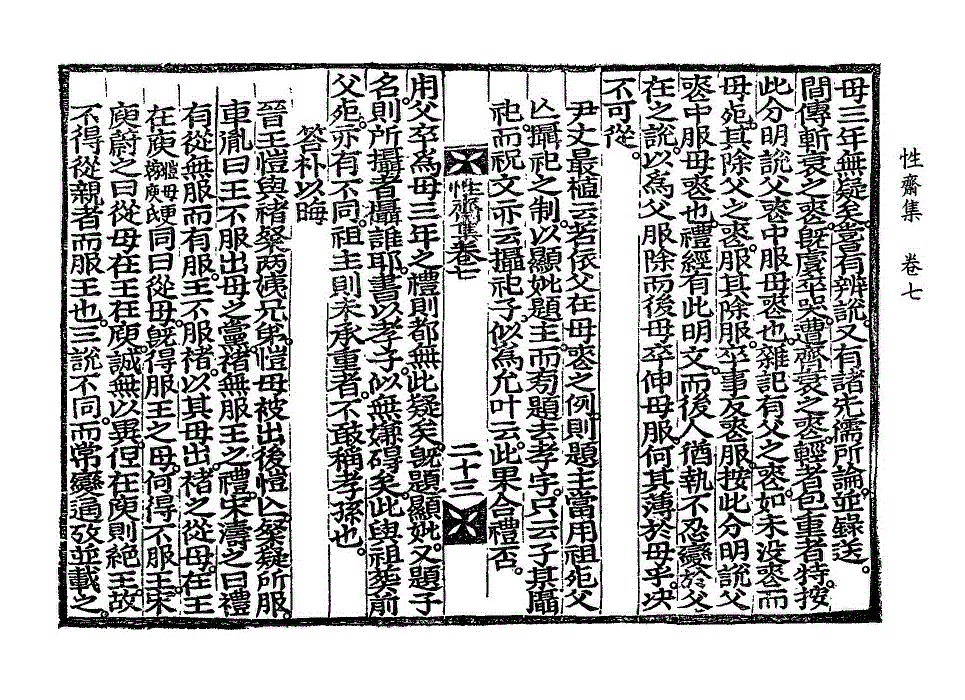 母三年无疑矣。尝有辨说。又有诸先儒所论。并录送。
母三年无疑矣。尝有辨说。又有诸先儒所论。并录送。间传斩衰之丧。既虞卒哭。遭齐衰之丧。轻者包重者特。按此分明说父丧中服母丧也。杂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按此分明说父丧中服母丧也。礼经有此明文。而后人犹执不忍变于父在之说。以为父服除而后母卒伸母服。何其薄于母乎。决不可从。
尹丈最植云若依父在母丧之例。则题主当用祖死父亡摄祀之制。以显妣题主。而旁题去孝字。只云子某摄祀。而祝文亦云摄祀子。似为允叶云。此果合礼否。
用父卒为母三年之礼则都无此疑矣。既题显妣。又题子名。则所摄者摄谁耶。书以孝子。似无嫌碍矣。此与祖葬前父死。亦有不同。祖主则未承重者。不敢称孝孙也。
答朴以晦
晋王恺与褚粲两姨兄弟。恺母被出后恺亡。粲疑所服。车胤曰王不服出母之党。褚无服王之礼。宋涛之曰礼有从无服而有服。王不服褚。以其母出。褚之从母。在王在庾(恺母更嫁庾氏)同曰从母。既得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宋庾蔚之曰从母在王在庾。诚无以异。但在庾则绝王。故不得从亲者而服王也。三说不同。而常变通考并载之。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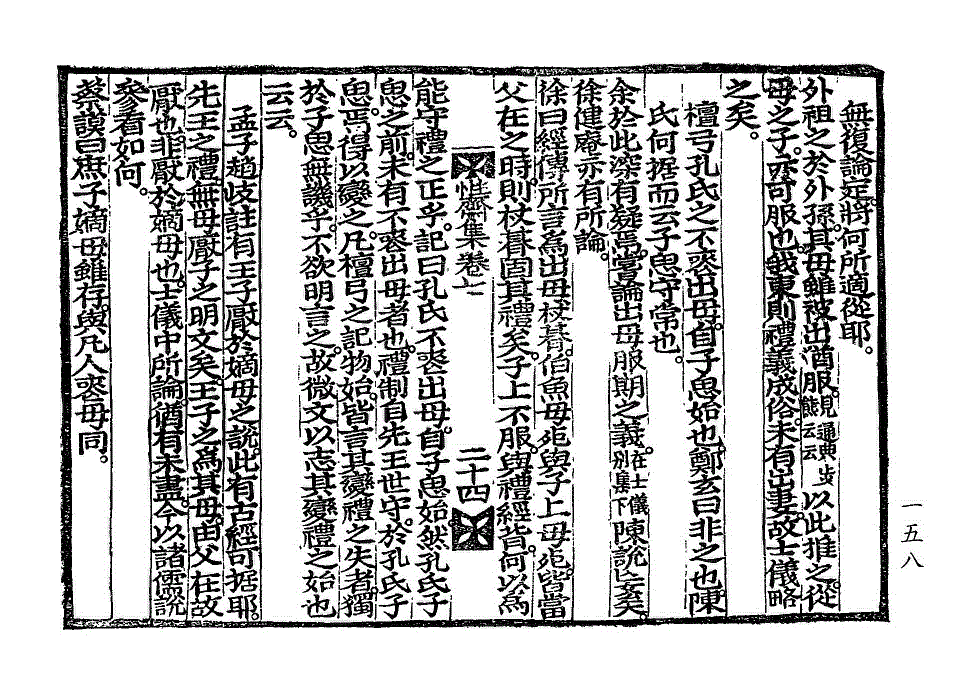 无复论定。将何所适从耶。
无复论定。将何所适从耶。外祖之于外孙。其母虽被出犹服。(见通典步熊云云)以此推之。从母之子。亦可服也。我东则礼义成俗。未有出妻。故士仪略之矣。
檀弓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郑玄曰非之也。陈氏何据而云子思守常也。
余于此深有疑焉。尝论出母服期之义。(在士仪别集下)陈说妄矣。徐健庵亦有所论。
徐曰经传所言为出母杖期。伯鱼母死与子上母死。皆当父在之时。则杖期固其礼矣。子上不服。与礼经背。何以为能守礼之正乎。记曰孔氏不丧出母。自子思始。然孔氏子思之前。未有不丧出母者也。礼制自先王世守。于孔氏子思。焉得以变之。凡檀弓之记物始。皆言其变礼之失者。独于子思无讥乎。不欲明言之。故微文以志其变礼之始也云云。
孟子赵岐注有王子厌于嫡母之说。此有古经可据耶。
先王之礼。无母厌子之明文矣。王子之为其母。由父在故厌也。非厌于嫡母也。士仪中所论。犹有未尽。今以诸儒说参看如何。
蔡谟曰庶子嫡母虽存。与凡人丧母同。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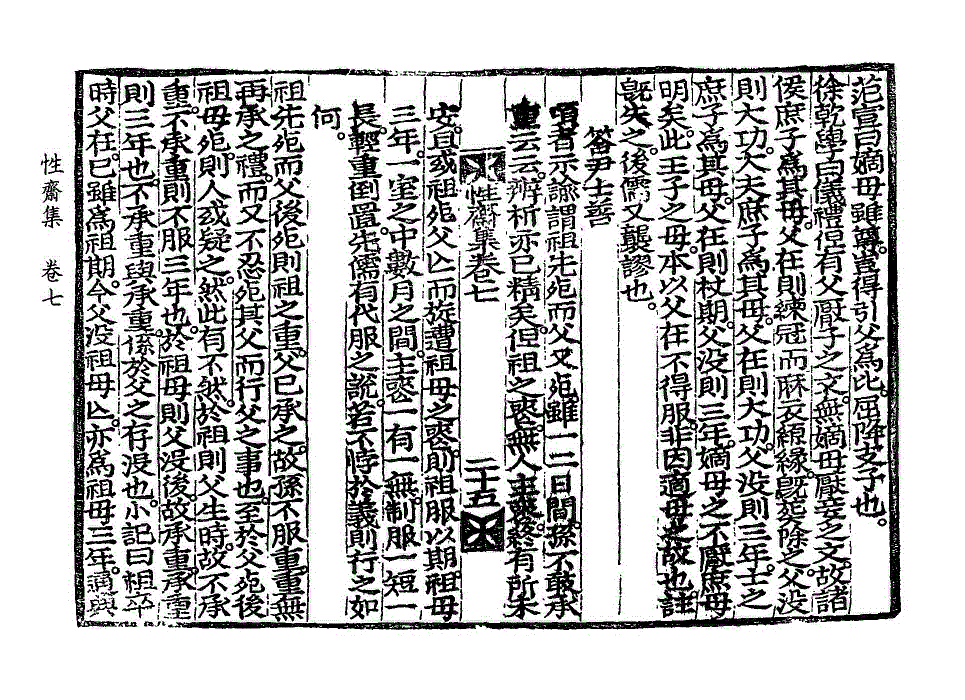 范宣曰嫡母虽尊。岂得引父为比。屈降支子也。
范宣曰嫡母虽尊。岂得引父为比。屈降支子也。徐乾学曰仪礼但有父厌子之文。无嫡母厌妾之文。故诸侯庶子为其母。父在则练冠而麻衣縓缘。既葬除之。父没则大功。大夫庶子为其母。父在则大功。父没则三年。士之庶子为其母。父在则杖期。父没则三年。嫡母之不厌庶母明矣。此王子之母。本以父在不得服。非因适母之故也。注既失之。后儒又袭谬也。
答尹士善
顷者示谕谓祖先死而父又死。虽一二日间。孙不敢承重云云。辨析亦已精矣。但祖之丧。无人主丧。终有所未安。且或祖死父亡而旋遭祖母之丧。则祖服以期。祖母三年。一室之中数月之间。主丧一有一无。制服一短一长。轻重倒置。先儒有代服之说。若不悖于义则行之如何。
祖先死而父后死则祖之重。父已承之。故孙不服重。重无再承之礼。而又不忍死其父而行父之事也。至于父死后祖母死。则人或疑之。然此有不然。于祖则父生时。故不承重。不承重则不服三年也。于祖母则父没后。故承重。承重则三年也。不承重与承重。系于父之存没也。小记曰祖卒时父在。己虽为祖期。今父没祖母亡。亦为祖母三年。通典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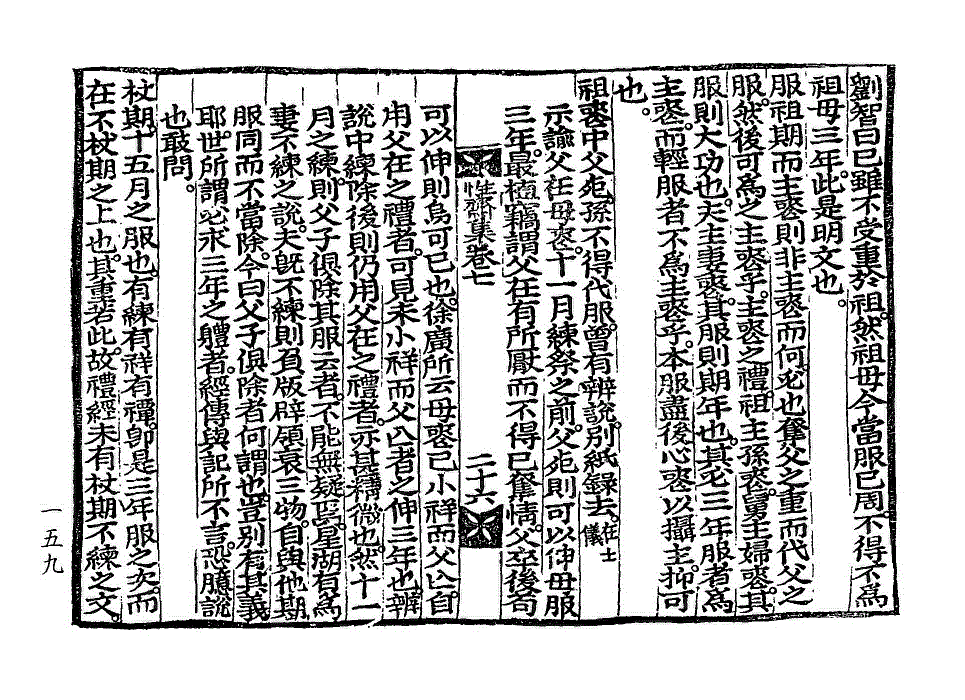 刘智曰己虽不受重于祖。然祖母今当服已周。不得不为祖母三年。此是明文也。
刘智曰己虽不受重于祖。然祖母今当服已周。不得不为祖母三年。此是明文也。服祖期而主丧则非主丧而何。必也夺父之重而代父之服。然后可为之主丧乎。主丧之礼。祖主孙丧。舅主妇丧。其服则大功也。夫主妻丧。其服则期年也。其必三年服者为主丧。而轻服者不为主丧乎。本服尽后心丧以摄主。抑可也。
祖丧中父死。孙不得代服。曾有辨说。别纸录去。(在士仪)
示谕父在母丧。十一月练祭之前。父死则可以伸母服三年。最植窃谓父在有所厌而不得已夺情。父卒后苟可以伸则乌可已也。徐广所云母丧已小祥而父亡。自用父在之礼者。可见未小祥而父亡者之伸三年也。辨说中练除后则仍用父在之礼者。亦甚精微也。然十一月之练。则父子俱除其服云者。不能无疑焉。星湖有为妻不练之说。夫既不练则负版辟领衰三物。自与他期服同而不当除。今曰父子俱除者何谓也。岂别有其义耶。世所谓必求三年之体者。经传与记所不言。恐臆说也敢问。
杖期。十五月之服也。有练有祥有禫。即是三年服之次。而在不杖期之上也。其重若此。故礼经未有杖期不练之文。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0H 页
 盖杖则练练则祥。杖未有不练也。但非三年之体也。后人泛看练祥禫之有似乎三年服。而不知杖期之自有练祥禫。互相纷纭也。不练之说。恐有所激于三年体之说。而未及细究耳。曾有所辨说。玆录去。
盖杖则练练则祥。杖未有不练也。但非三年之体也。后人泛看练祥禫之有似乎三年服。而不知杖期之自有练祥禫。互相纷纭也。不练之说。恐有所激于三年体之说。而未及细究耳。曾有所辨说。玆录去。负适衰三物。实是方领之制。所系非但表其哀而已也。虽功缌之服。终始不可无者也。后人之不究经义而去之者。何可从也。礼经但言既练。男子除乎首。妇人除乎腰。此不过首腰之绖带。更何有他物除去之證乎。温公书仪偶失之。家礼因书仪而未及修正。故杨慎斋亦曰丧服记载衰负版辟领之制。但不言何时而除。家礼据书仪小祥去之。又曰有阙文。又曰疏略。此可以类推也。
徐健庵读礼通考曰丧服经大功小功。皆言布衰裳缌麻。注疏亦言布衰裳。则五服未有不用衰者。郑注言五服之衰。一斩四缉。凡言衰者。总五服而言。开元礼政和礼以下俱言衰裳。温公书仪齐衰不用衰。易以宽袖襕衫。朱子家礼大功以下不用衰。于是轻丧不知有衰矣。
松江上海县。见有功缌丧者。皆准古礼制衰服。风俗淳厚云云。
丧服传曰有嫡子者。无嫡孙。孙妇亦如之。退溪亦谓祖母或母服重服。妻不得服重。后来儒贤皆据此为定。近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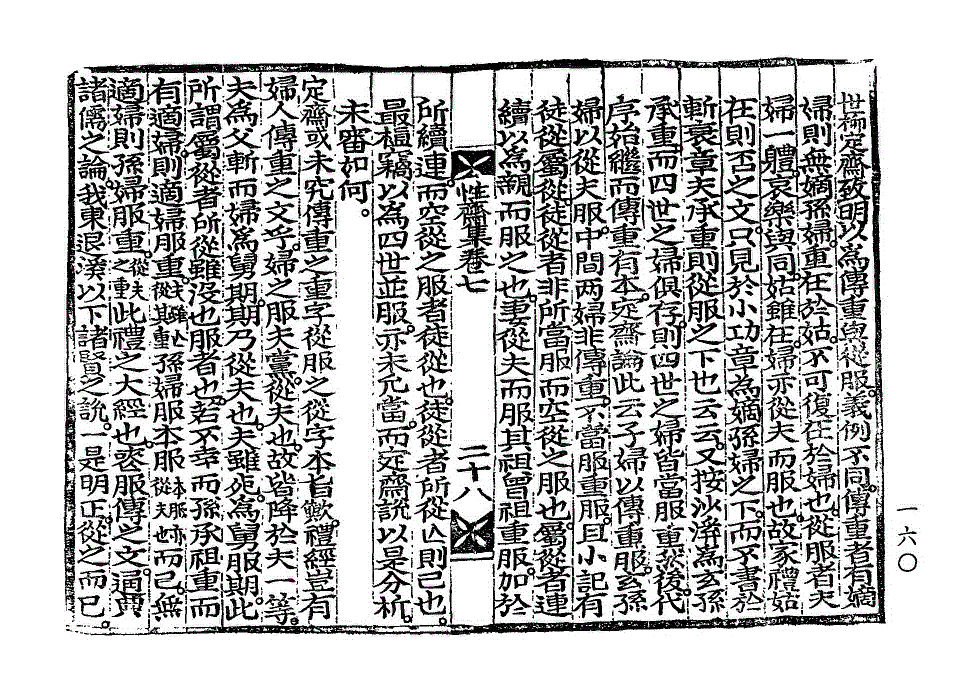 世柳定斋致明以为传重与从服。义例不同。传重者有嫡妇则无嫡孙妇。重在于姑。不可复在于妇也。从服者夫妇一体。哀乐与同。姑虽在。妇亦从夫而服也。故家礼姑在则否之文。只见于小功章为嫡孙妇之下。而不书于斩衰章夫承重则从服之下也云云。又按沙溪为玄孙承重。而四世之妇俱存。则四世之妇皆当服重然后。代序始继而传重有本。定斋论此云子妇以传重服。玄孙妇以从夫服。中间两妇非传重。不当服重服。且小记有徒从属从。徒从者非所当服而空从之服也。属从者连续以为亲而服之也。妻从夫而服其祖曾祖重服。加于所续连。而空从之服者徒从也。徒从者所从亡则已也。最植窃以为四世并服。亦未允当。而定斋说以是分析。未审如何。
世柳定斋致明以为传重与从服。义例不同。传重者有嫡妇则无嫡孙妇。重在于姑。不可复在于妇也。从服者夫妇一体。哀乐与同。姑虽在。妇亦从夫而服也。故家礼姑在则否之文。只见于小功章为嫡孙妇之下。而不书于斩衰章夫承重则从服之下也云云。又按沙溪为玄孙承重。而四世之妇俱存。则四世之妇皆当服重然后。代序始继而传重有本。定斋论此云子妇以传重服。玄孙妇以从夫服。中间两妇非传重。不当服重服。且小记有徒从属从。徒从者非所当服而空从之服也。属从者连续以为亲而服之也。妻从夫而服其祖曾祖重服。加于所续连。而空从之服者徒从也。徒从者所从亡则已也。最植窃以为四世并服。亦未允当。而定斋说以是分析。未审如何。定斋或未究传重之重字从服之从字本旨欤。礼经岂有妇人传重之文乎。妇之服夫党。从夫也。故皆降于夫一等。夫为父斩而妇为舅期。期乃从夫也。夫虽死。为舅服期。此所谓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者也。若不幸而孙承祖重而有适妇。则适妇服重。(夫虽亡从其重)孙妇服本服(本服亦从夫也)而已。无适妇则孙妇服重。(从夫之重)此礼之大经也。丧服传之文。通典诸儒之论。我东退溪以下诸贤之说。一是明正。从之而已。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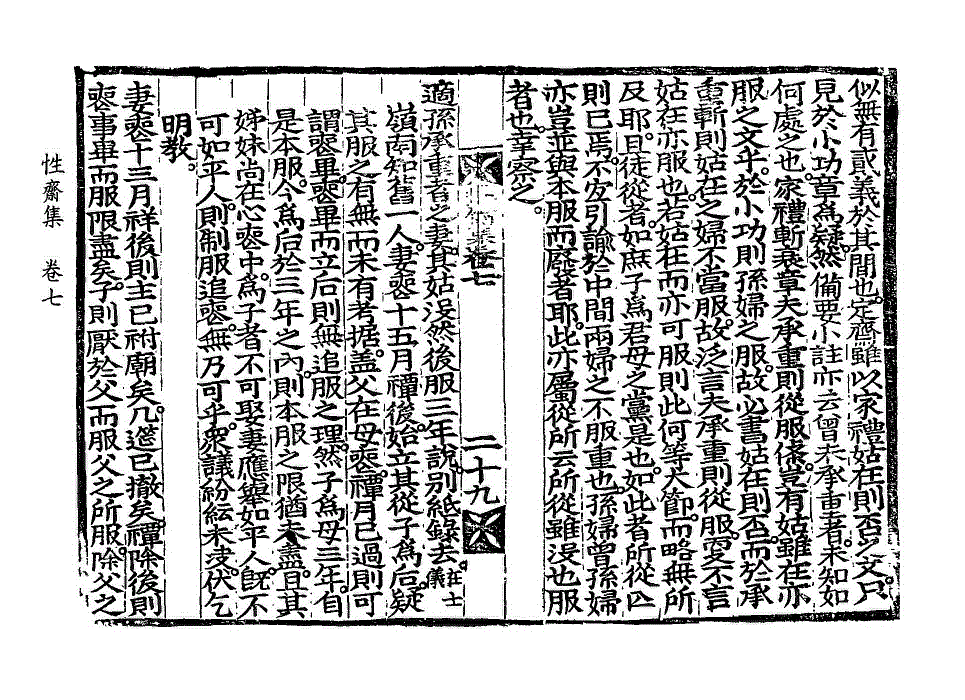 似无有贰义于其间也。定斋虽以家礼姑在则否之文。只见于小功章为疑。然备要小注亦云曾未承重者。未知如何处之也。家礼斩衰章夫承重则从服条。岂有姑虽在亦服之文乎。于小功则孙妇之服。故必书姑在则否。而于承重斩则姑在之妇不当服。故泛言夫承重则从服。更不言姑在亦服也。若姑在而亦可服则此何等大节。而略无所及耶。且徒从者。如庶子为君母之党是也。如此者所从亡则已焉。不宜引谕于中间两妇之不服重也。孙妇曾孙妇亦岂并与本服而废者耶。此亦属从所云所从虽没也服者也。幸察之。
似无有贰义于其间也。定斋虽以家礼姑在则否之文。只见于小功章为疑。然备要小注亦云曾未承重者。未知如何处之也。家礼斩衰章夫承重则从服条。岂有姑虽在亦服之文乎。于小功则孙妇之服。故必书姑在则否。而于承重斩则姑在之妇不当服。故泛言夫承重则从服。更不言姑在亦服也。若姑在而亦可服则此何等大节。而略无所及耶。且徒从者。如庶子为君母之党是也。如此者所从亡则已焉。不宜引谕于中间两妇之不服重也。孙妇曾孙妇亦岂并与本服而废者耶。此亦属从所云所从虽没也服者也。幸察之。适孙承重者之妻。其姑没然后服三年说。别纸录去。(在士仪)
岭南知旧一人。妻丧十五月禫后。始立其从子为后。疑其服之有无而未有考据。盖父在母丧。禫月已过则可谓丧毕。丧毕而立后则无追服之理。然子为母三年。自是本服。今为后于三年之内。则本服之限犹未尽。且其姊妹尚在心丧中。为子者不可娶妻应举如平人。既不可如平人。则制服追丧。无乃可乎。众议纷纭未决。伏乞明教。
妻丧十三月祥后则主已祔庙矣。几筵已撤矣。禫除后则丧事毕而服限尽矣。子则厌于父而服父之所服。除父之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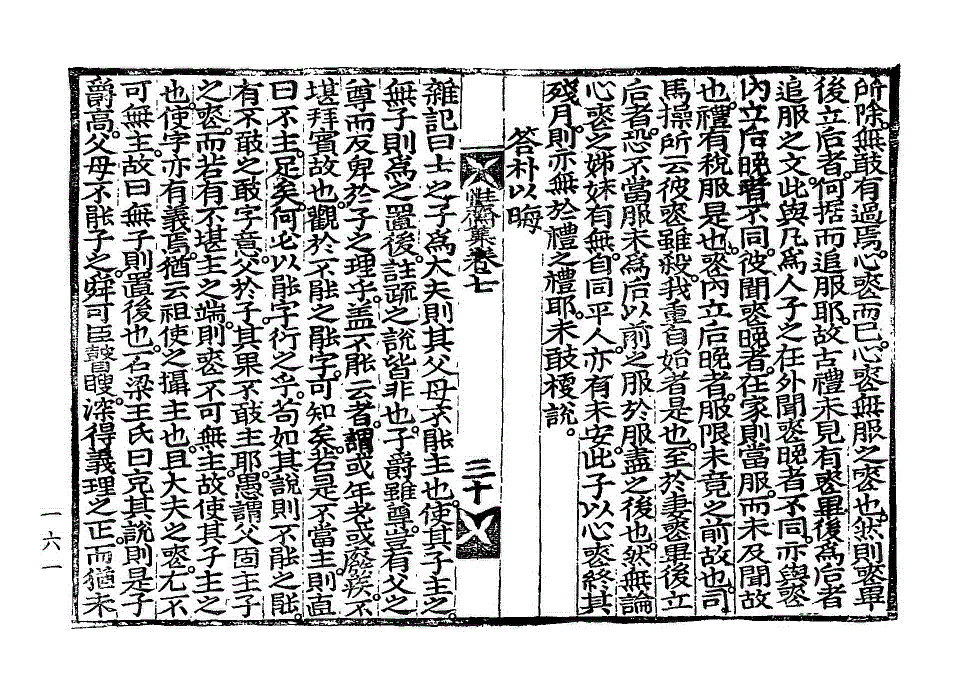 所除。无敢有过焉。心丧而已。心丧无服之丧也。然则丧毕后立后者。何据而追服耶。故古礼未见有丧毕后为后者追服之文。此与凡为人子之在外闻丧晚者不同。亦与丧内立后晚者不同。彼闻丧晚者。在家则当服。而未及闻故也。礼有税服是也。丧内立后晚者。服限未竟之前故也。司马操所云彼丧虽杀。我重自始者是也。至于妻丧毕后立后者。恐不当服未为后以前之服于服尽之后也。然无论心丧之姊妹有无。自同平人。亦有未安。此子以心丧终其残月。则亦无于礼之礼耶。未敢梗说。
所除。无敢有过焉。心丧而已。心丧无服之丧也。然则丧毕后立后者。何据而追服耶。故古礼未见有丧毕后为后者追服之文。此与凡为人子之在外闻丧晚者不同。亦与丧内立后晚者不同。彼闻丧晚者。在家则当服。而未及闻故也。礼有税服是也。丧内立后晚者。服限未竟之前故也。司马操所云彼丧虽杀。我重自始者是也。至于妻丧毕后立后者。恐不当服未为后以前之服于服尽之后也。然无论心丧之姊妹有无。自同平人。亦有未安。此子以心丧终其残月。则亦无于礼之礼耶。未敢梗说。答朴以晦
杂记曰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不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后。注疏之说皆非也。子爵虽尊。岂有父之尊而反卑于子之理乎。盖不能云者。谓或年老或废疾。不堪拜宾故也。观于不能之能字。可知矣。若是不当主。则直曰不主。足矣。何必以能字行之乎。苟如其说则不能之能。有不敢之敢字意。父于子。其果不敢主耶。愚谓父固主子之丧。而若有不堪主之端。则丧不可无主。故使其子主之也。使字亦有义焉。犹云祖使之摄主也。且大夫之丧。尤不可无主。故曰无子则置后也。石梁王氏曰充其说则是子爵高。父母不能子之。舜可臣𥌒瞍。深得义理之正。而犹未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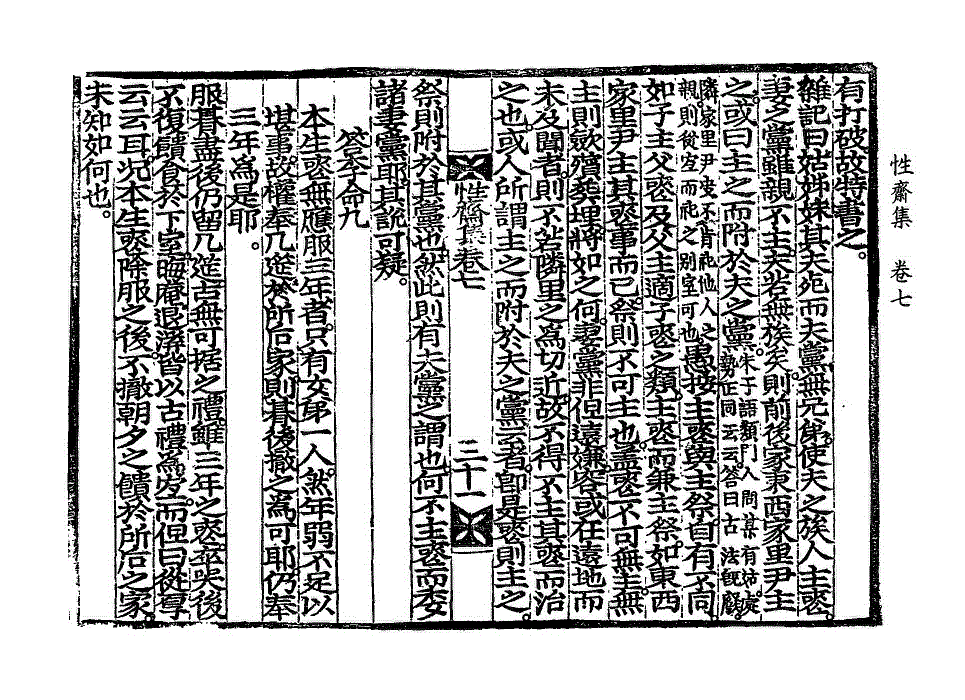 有打破。故特书之。
有打破。故特书之。杂记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不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朱子语类门人问某有姑。处势正同云云。答曰古法既废。邻家里尹决不肯祀他人之亲。则从宜而祀之别室可也。)愚按主丧与主祭。自有不同。如子主父丧及父主适子丧之类。主丧而兼主祭。如东西家里尹主其丧事而已。祭则不可主也。盖丧不可无主。无主则敛殡葬埋。将如之何。妻党非但远嫌。容或在远地而未及闻者。则不若邻里之为切近。故不得不主其丧而治之也。或人所谓主之而附于夫之党云者。即是丧则主之。祭则附于其党也。然此则有夫党之谓也。何不主丧而委诸妻党耶。其说可疑。
答李命九
本生丧无应服三年者。只有女弟一人。然年弱不足以堪事。故权奉几筵于所后家。则期后撤之为可耶。仍奉三年为是耶。
服期尽后仍留几筵。古无可据之礼。虽三年之丧。卒哭后不复馈食于下室。晦庵,退溪皆以古礼为宜。而但曰从厚云云耳。况本生丧除服之后。不撤朝夕之馈于所后之家。未知如何也。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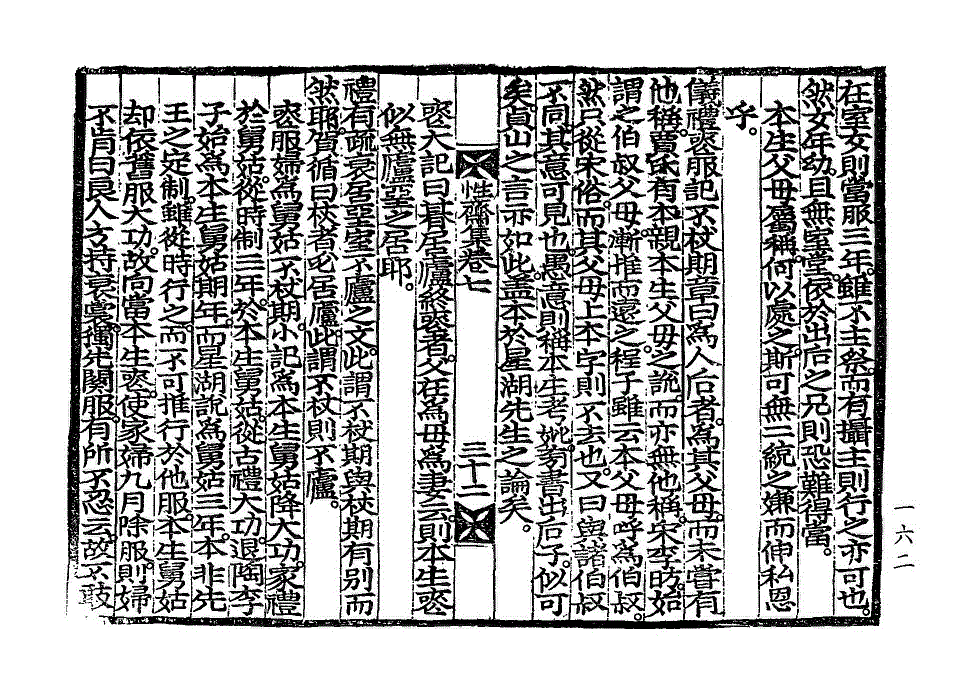 在室女则当服三年。虽不主祭。而有摄主则行之亦可也。然女年幼。且无室堂。依于出后之兄则恐难得当。
在室女则当服三年。虽不主祭。而有摄主则行之亦可也。然女年幼。且无室堂。依于出后之兄则恐难得当。本生父母属称。何以处之。斯可无二统之嫌而伸私恩乎。
仪礼丧服记不杖期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而未尝有他称。贾氏有本亲本生父母之说。而亦无他称。宋李昉。始谓之伯叔父母。渐推而远之。程子虽云本父母呼为伯叔。然只从宋俗。而其父母上本字则不去也。又曰与诸伯叔不同。其意可见也。愚意则称本生考妣。旁书出后子。似可矣。贞山之言亦如此。盖本于星湖先生之论矣。
丧大记曰期居庐终丧者。父在为母为妻云。则本生丧似无庐垩之居耶。
礼有疏衰居垩室不庐之文。此谓不杖期与杖期有别而然耶。贺循曰杖者必居庐。此谓不杖则不庐。
丧服妇为舅姑不杖期。小记为本生舅姑降大功。家礼于舅姑。从时制三年。于本生舅姑。从古礼大功。退陶李子始为本生舅姑期年。而星湖说为舅姑三年。本非先王之定制。虽从时行之。而不可推行于他服。本生舅姑却依旧服大功。故向当本生丧。使家妇九月除服。则妇不肯曰良人方持衰裳。独先阕服。有所不忍云。故不敢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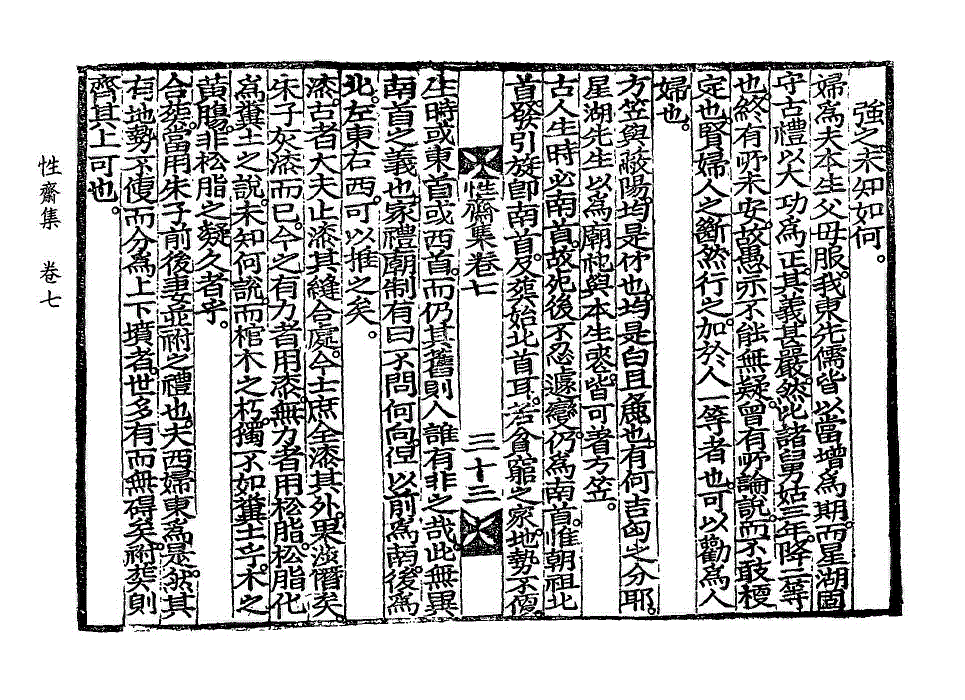 强之。未知如何。
强之。未知如何。妇为夫本生父母服。我东先儒皆以当增为期。而星湖固守古礼以大功为正。其义甚严。然比诸舅姑三年。降二等也。终有所未安。故愚亦不能无疑。曾有所论说。而不敢梗定也。贤妇人之断然行之。加于人一等者也。可以劝为人妇也。
方笠与蔽阳。均是竹也。均是白且粗也。有何吉匈之分耶。星湖先生以为庙祀与本生丧。皆可着方笠。
古人生时必南首。故死后不忍遽变。仍为南首。惟朝祖北首。发引旋即南首。及葬始北首耳。若贫穷之家。地势不便。生时或东首或西首。而仍其旧则人谁有非之哉。此无异南首之义也。家礼庙制有曰不问何向。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东右西。可以推之矣。
漆。古者大夫止漆其缝合处。今士庶全漆其外。果涉僭矣。朱子灰漆而已。今之有力者用漆。无力者用松脂。松脂化为粪土之说。未知何说。而棺木之朽。独不如粪土乎。木之黄肠。非松脂之凝久者乎。
合葬。当用朱子前后妻并祔之礼也。夫西妇东为是。然其有地势不便而分为上下坟者。世多有而无碍矣。祔葬则齐其上可也。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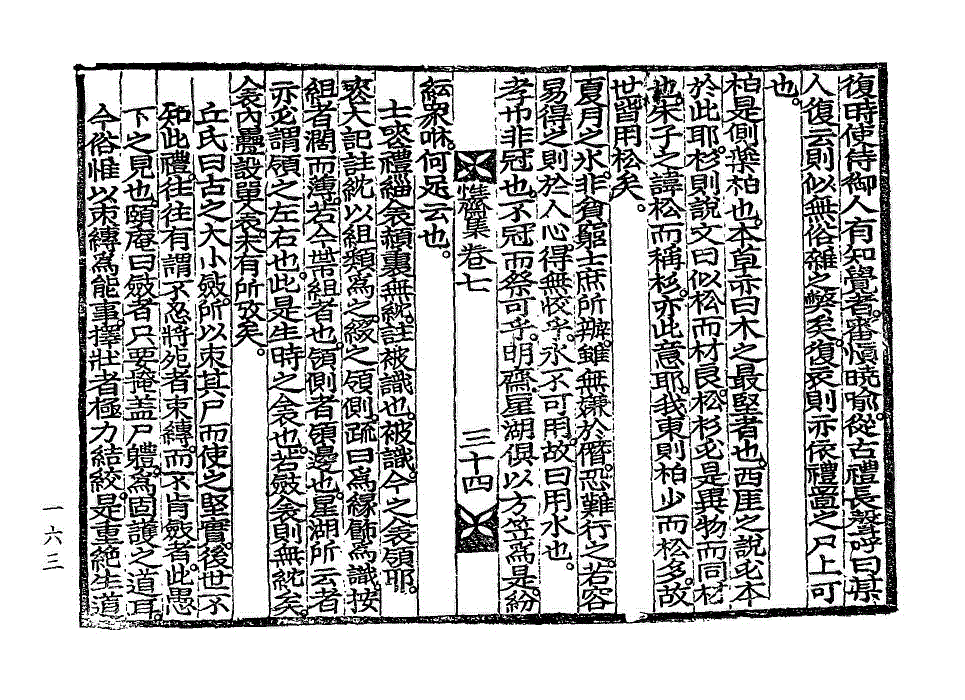 复时使侍御人有知觉者。审慎晓喻。从古礼长声呼曰某人复云则似无俗杂之弊矣。复衣则亦依礼置之尸上可也。
复时使侍御人有知觉者。审慎晓喻。从古礼长声呼曰某人复云则似无俗杂之弊矣。复衣则亦依礼置之尸上可也。柏是侧叶柏也。本草亦曰木之最坚者也。西厓之说必本于此耶。杉则说文曰似松而材良。松杉必是异物而同材也。朱子之讳松而称杉。亦此意耶。我东则柏少而松多。故世皆用松矣。
夏月之冰。非贫穷士庶所办。虽无嫌于僭。恐难行之。若容易得之则于人心。得无恔乎。冰不可用。故曰用水也。
孝巾非冠也。不冠而祭可乎。明斋,星湖俱以方笠为是。纷纭众咻。何足云也。
士丧礼缁衾赪里无紞。注被识也。被识。今之衾领耶。
丧大记注紞以组类为之。缀之领侧。疏曰为缘饰为识。按组者阔而薄。若今带组者也。领侧者领边也。星湖所云者亦必谓领之左右也。此是生时之衾也。若敛衾则无紞矣。衾内叠设单衾。未有所考矣。
丘氏曰古之大小敛。所以束其尸而使之坚实。后世不知此礼。往往有谓不忍将死者束缚。而不肯敛者。此愚下之见也。颐庵曰敛者只要掩盖尸体。为固护之道耳。今俗惟以束缚为能事。择壮者极力结绞。是重绝生道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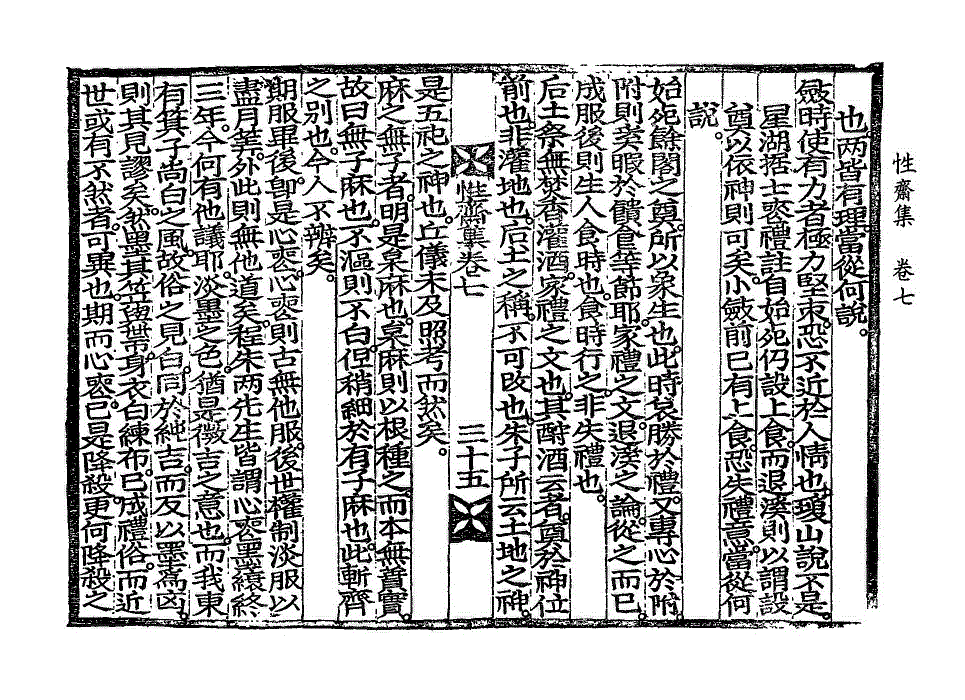 也。两皆有理。当从何说。
也。两皆有理。当从何说。敛时使有力者极力坚束。恐不近于人情也。琼山说不是。
星湖据士丧礼注自始死仍设上食。而退溪则以谓设奠以依神则可矣。小敛前已有上食。恐失礼意。当从何说。
始死馀阁之奠。所以象生也。此时哀胜于礼。又专心于附。附则奚暇于馈食等节耶。家礼之文。退溪之论。从之而已。成服后则生人食时也。食时行之。非失礼也。
后土祭无焚香灌酒。家礼之文也。其酬酒云者。奠于神位前也。非灌地也。后土之称。不可改也。朱子所云土地之神。是五祀之神也。丘仪未及照考而然矣。
麻之无子者。明是枲麻也。枲麻则以根种之。而本无蕡实。故曰无子麻也。不沤则不白。但稍细于有子麻也。此斩齐之别也。今人不辨矣。
期服毕后。即是心丧。心丧则古无他服。后世权制淡服以尽月算。外此则无他道矣。程朱两先生皆谓心丧墨缞终三年。今何有他议耶。淡墨之色。犹是微吉之意也。而我东有箕子尚白之风。故俗之见白。同于纯吉。而反以墨为凶。则其见谬矣。然墨其笠与带。身衣白练布。已成礼俗。而近世或有不然者。可异也。期而心丧。已是降杀。更何降杀之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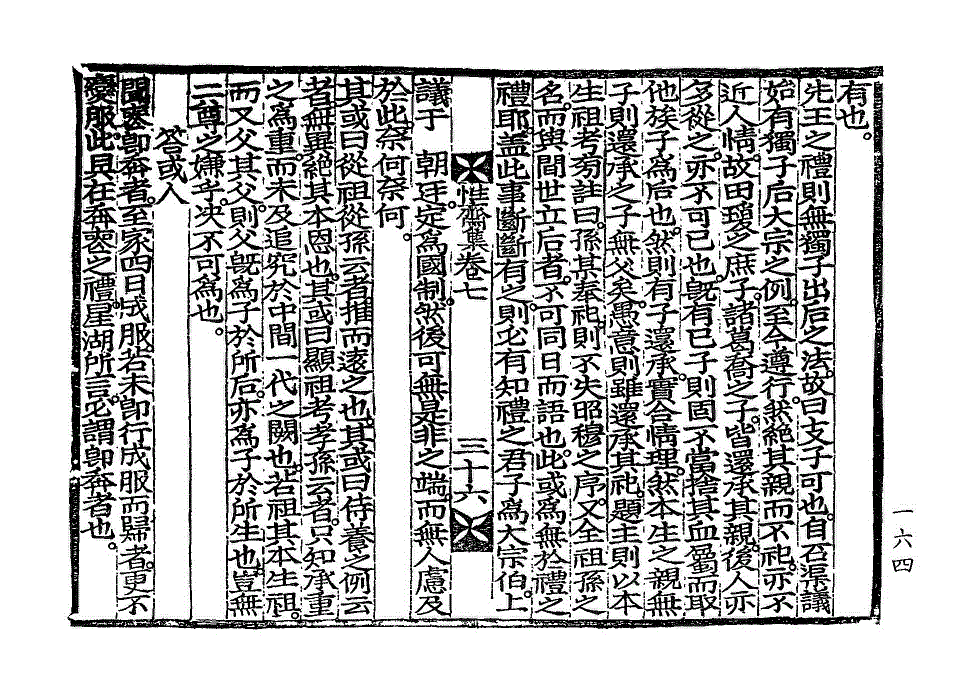 有也。
有也。先王之礼则无独子出后之法。故曰支子可也。自石渠议始有独子后大宗之例。至今遵行。然绝其亲而不祀。亦不近人情。故田琼之庶子。诸葛乔之子。皆还承其亲。后人亦多从之。亦不可已也。既有己子则固不当舍其血属而取他族子为后也。然则有子还承。实合情理。然本生之亲无子则还承之子无父矣。愚意则虽还承其祀。题主则以本生祖考旁注曰。孙某奉祀。则不失昭穆之序。又全祖孙之名。而与间世立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此或为无于礼之礼耶。盖此事断断有之。则必有知礼之君子为大宗伯。上议于 朝廷。定为国制。然后可无是非之端。而无人虑及于此。奈何奈何。
其或曰从祖从孙云者。推而远之也。其或曰侍养之例云者。无异绝其本恩也。其或曰显祖考孝孙云者。只知承重之为重。而未及追究于中间一代之阙也。若祖其本生祖。而又父其父。则父既为子于所后。亦为子于所生也。岂无二尊之嫌乎。决不可为也。
答或人
闻丧即奔者。至家四日成服。若未即行成服而归者。更不变服。此具在奔丧之礼。星湖所言。必谓即奔者也。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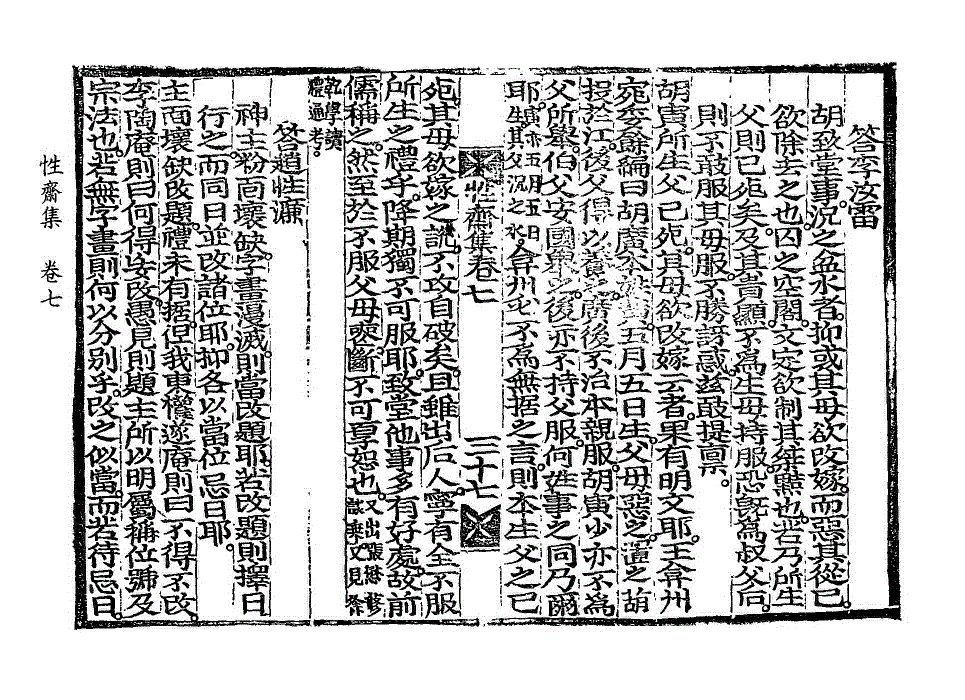 答李汝雷
答李汝雷胡致堂事。沉之盆水者。抑或其母欲改嫁。而恶其从己。欲除去之也。囚之空阁。文定欲制其桀黠也。若乃所生父则已死矣。及其贵显。不为生母持服。恐既为叔父后。则不敢服其母服。不胜讶惑。玆敢提禀。
胡寅所生父已死。其母欲改嫁云者。果有明文耶。王弇州宛委馀编曰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之葫投于江。后父得以养之。广后不治本亲服。胡寅少亦不为父所举。伯父安国举之。后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乃尔耶。(寅亦五月五日生。其父沉之水。)弇州必不为无据之言。则本生父之已死。其母欲嫁之说。不攻自破矣。且虽出后人。宁有全不服所生之礼乎。降期独不可服耶。致堂他事多有好处。故前儒称之。然至于不服父母丧。断不可厚恕也。(又出张懋修谈乘。又见徐乾学读礼通考。)
答赵性濂
神主粉面坏缺。字画漫灭。则当改题耶。若改题则择日行之。而同日并改诸位耶。抑各以当位忌日耶。
主面坏缺改题。礼未有据。但我东权遂庵则曰不得不改。李陶庵则曰何得妄改。愚见则题主所以明属称位号及宗法也。若无字画则何以分别乎。改之似当。而若待忌日。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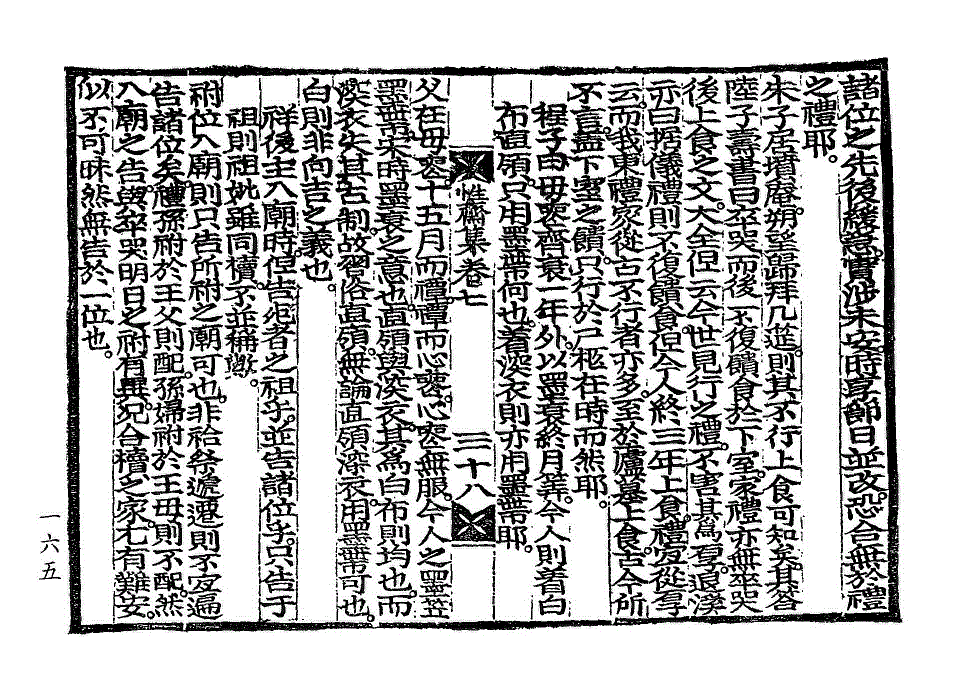 诸位之先后缓急。实涉未安。时享节日并改。恐合无于礼之礼耶。
诸位之先后缓急。实涉未安。时享节日并改。恐合无于礼之礼耶。朱子居坟庵。朔望归拜几筵。则其不行上食可知矣。其答陆子寿书曰卒哭而后不复馈食于下室。家礼亦无卒哭后上食之文。大全但云今世见行之礼。不害其为厚。退溪亦曰据仪礼则不复馈食。但今人终三年上食。礼宜从厚云。而我东礼家从古不行者亦多。至于庐墓上食。古今所不言。盖下室之馈。只行于尸柩在时而然耶。
程子曰母丧齐衰一年外。以墨衰终月算。今人则着白布直领。只用墨带何也。着深衣则亦用墨带耶。
父在母丧。十五月而禫。禫而心丧。心丧无服。今人之墨笠墨带。宋时墨衰之意也。直领与深衣。其为白布则均也。而深衣失其古制。故习俗直领。无论直领深衣。用墨带可也。白则非向吉之义也。
祥后主入庙时。但告死者之祖乎。并告诸位乎。只告于祖则祖妣虽同椟。不并称欤。
祔位入庙则只告所祔之庙可也。非祫祭递迁则不宜遍告诸位矣。礼孙祔于王父则配。孙妇祔于王母则不配。然入庙之告。与卒哭明日之祔有异。况合椟之家。尤有难安。似不可昧然无告于一位也。
答姜判书(兰馨)
侍生之堂叔。今初七日(正月)丧出。而于侍生为曾高祖奉祀之孙也。曾高祠版。以其贫穷。权奉于侍生家矣。今望日茶礼及二十二日忌祭。当设行否。
礼曰所祭于死者无服则祭。尊堂叔既为高曾之嗣孙则有服矣。今虽丧出异宫。而支孙权奉祠版。然摄祀之礼。必以宗子名祭之。事虽难便。恐不可祭。幸博询处之如何。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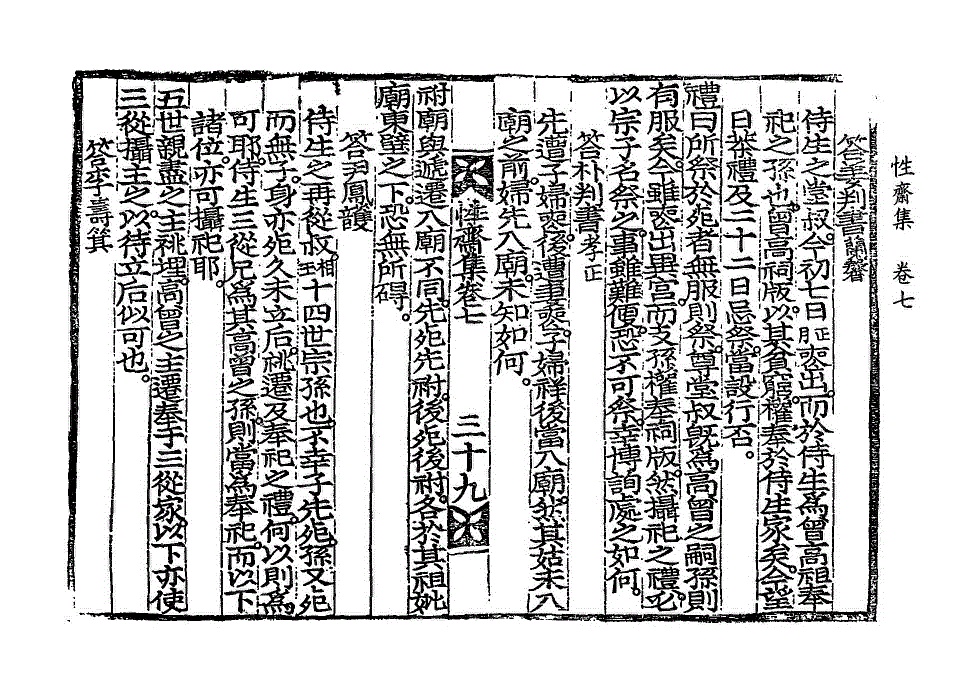 答朴判书(孝正)
答朴判书(孝正)先遭子妇丧。后遭妻丧。子妇祥后当入庙。然其姑未入庙之前。妇先入庙。未知如何。
祔庙与递迁入庙不同。先死先祔。后死后祔。各于其祖妣庙东壁之下。恐无所碍。
答尹凤頀
侍生之再从叔。(相玉)十四世宗孙也。不幸子先死。孙又死而无子。身亦死久未立后。祧迁及奉祀之礼。何以则为可耶。侍生三从兄为其高曾之孙。则当为奉祀。而以下诸位。亦可摄祀耶。
五世亲尽之主祧埋。高曾之主迁奉于三从家。以下亦使三从摄主之。以待立后似可也。
答李寿箕
性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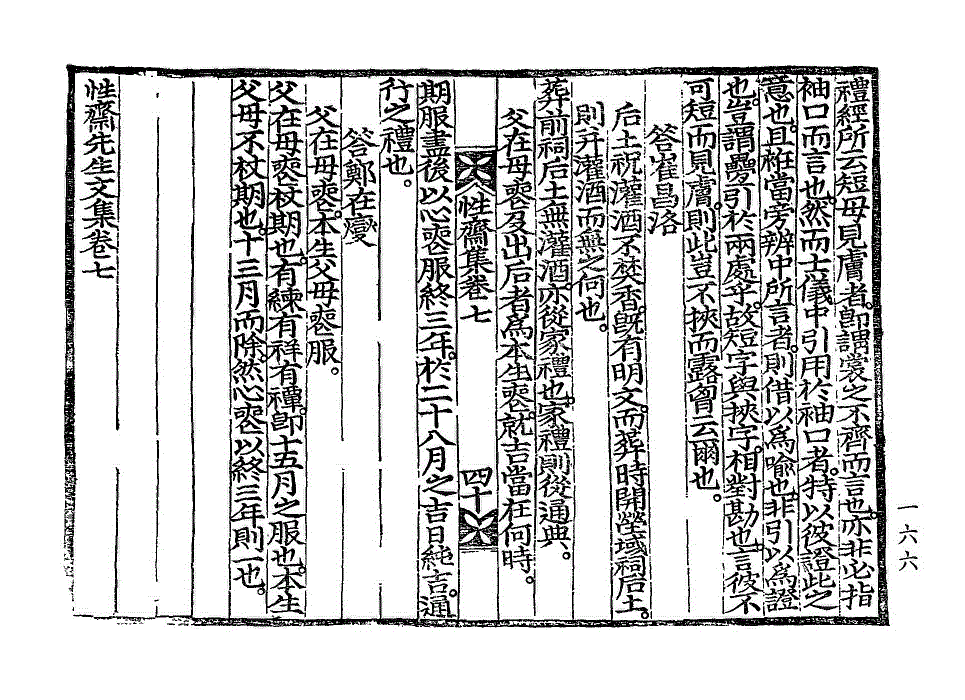 礼经所云短毋见肤者。即谓裳之不齐而言也。亦非必指袖口而言也。然而士仪中引用于袖口者。特以彼證此之意也。且衽当旁辨中所言者。则借以为喻也。非引以为證也。岂谓叠引于两处乎。故短字与挟字。相对勘也。言彼不可短而见肤。则此岂不挟而露胸云尔也。
礼经所云短毋见肤者。即谓裳之不齐而言也。亦非必指袖口而言也。然而士仪中引用于袖口者。特以彼證此之意也。且衽当旁辨中所言者。则借以为喻也。非引以为證也。岂谓叠引于两处乎。故短字与挟字。相对勘也。言彼不可短而见肤。则此岂不挟而露胸云尔也。答崔昌洛
后土祝灌酒不焚香。既有明文。而葬时开茔域祠后土。则并灌酒而无之何也。
葬前祠后土无灌酒。亦从家礼也。家礼则从通典。
父在母丧及出后者为本生丧。就吉当在何时。
期服尽后以心丧服终三年。于二十八月之吉日纯吉。通行之礼也。
答郑在燮
父在母丧。本生父母丧服。
父在母丧杖期也。有练有祥有禫。即十五月之服也。本生父母不杖期也。十三月而除。然心丧以终三年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