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x 页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语录
语录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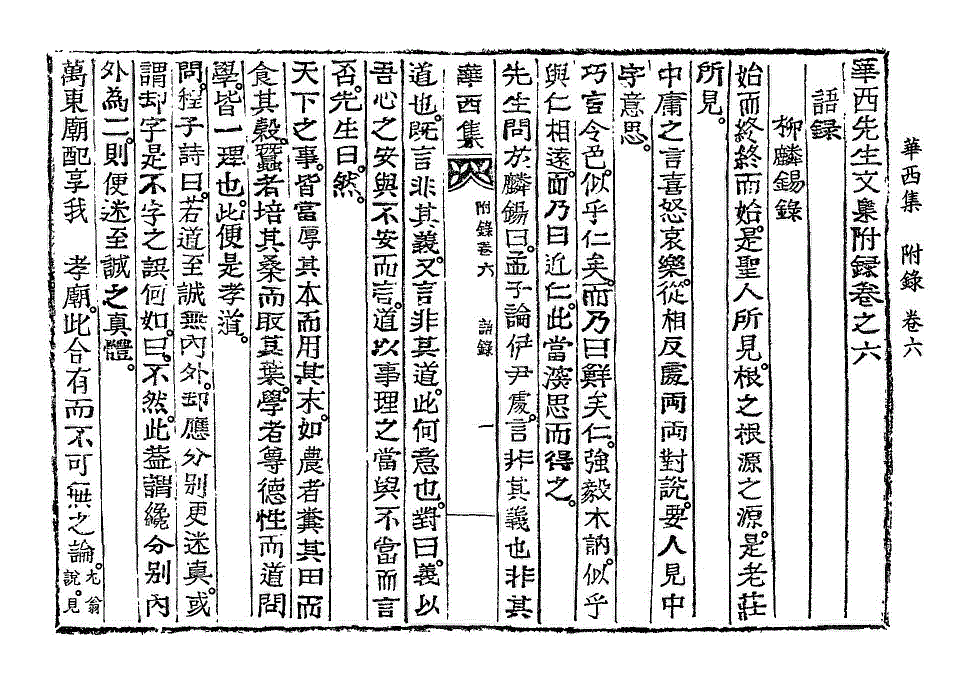 柳麟锡录
柳麟锡录始而终终而始。是圣人所见。根之根源之源。是老庄所见。
中庸之言喜怒哀乐。从相反处两两对说。要人见中字意思。
巧言令色。似乎仁矣。而乃曰鲜矣仁。强毅木讷。似乎与仁相远。而乃曰近仁。此当深思而得之。
先生问于麟锡曰。孟子论伊尹处。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既言非其义。又言非其道。此何意也。对曰。义以吾心之安与不安而言。道以事理之当与不当而言否。先生曰。然。
天下之事。皆当厚其本而用其末。如农者粪其田而食其谷。蚕者培其桑而取其叶。学者尊德性而道问学。皆一理也。此便是孝道。
问。程子诗曰。若道至诚无内外。却应分别更迷真。或谓却字是不字之误何如。曰。不然。此盖谓才分别内外为二。则便迷至诚之真体。
万东庙配享我 孝庙。此合有而不可无之论。(尤翁说。见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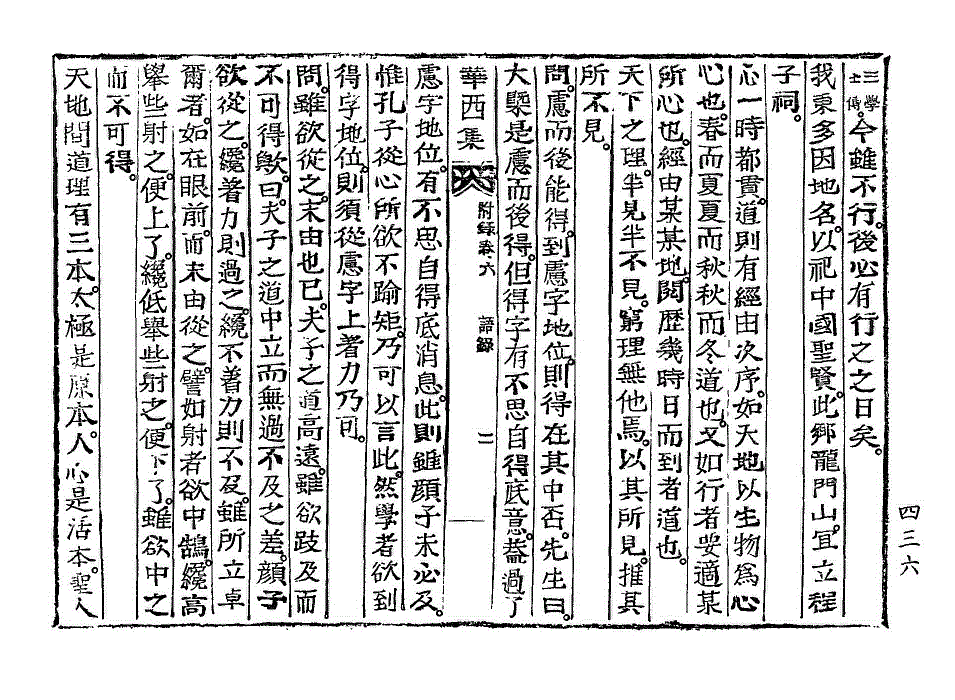 三学士传。)今虽不行。后必有行之之日矣。
三学士传。)今虽不行。后必有行之之日矣。我东多因地名。以祀中国圣贤。此乡龙门山。宜立程子祠。
心一时都贯。道则有经由次序。如天地以生物为心心也。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道也。又如行者要适某所心也。经由某某地。阅历几时日而到者道也。
天下之理。半见半不见。穷理无他焉。以其所见。推其所不见。
问。虑而后能得。到虑字地位。则得在其中否。先生曰。大槩是虑而后得。但得字有不思自得底意。盖过了虑字地位。有不思自得底消息。此则虽颜子未必及。惟孔子从心所欲不踰矩。乃可以言此。然学者欲到得字地位。则须从虑字上着力乃可。
问。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夫子之道高远。虽欲跂及而不可得欤。曰。夫子之道中立而无过不及之差。颜子欲从之。才着力则过之。才不着力则不及。虽所立卓尔者。如在眼前。而末由从之。譬如射者欲中鹄。才高举些射之。便上了。才低举些射之。便下了。虽欲中之而不可得。
天地间道理有三本。太极是原本。人心是活本。圣人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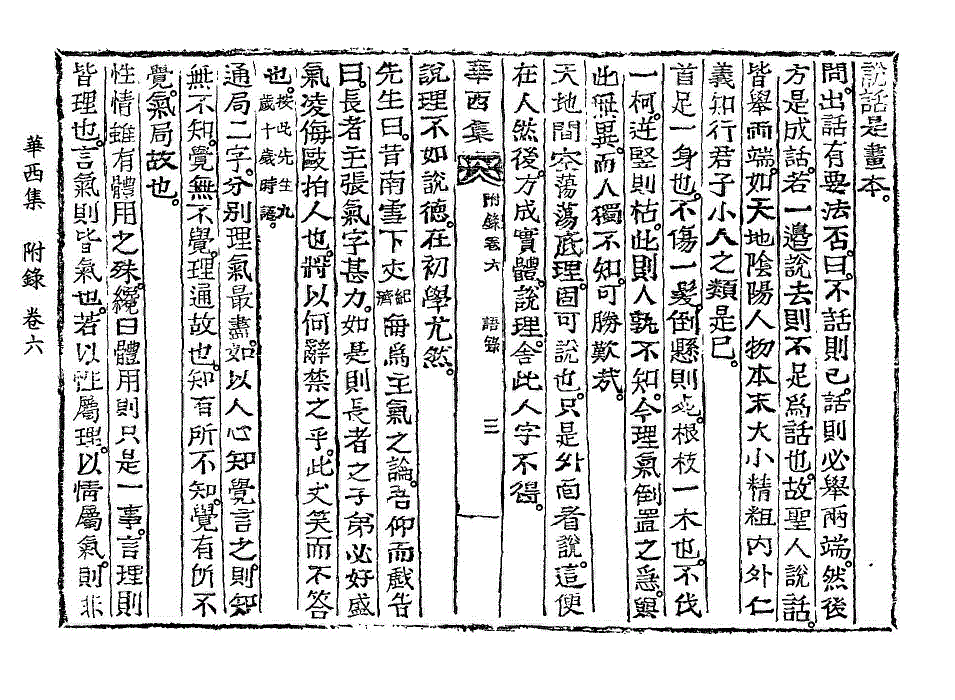 说话是画本。
说话是画本。问。出话有要法否。曰。不话则已。话则必举两端。然后方是成话。若一边说去则不足为话也。故圣人说话。皆举两端。如天地阴阳人物本末大小精粗内外仁义知行君子小人之类是已。
首足一身也。不伤一发。倒悬则死。根枝一木也。不伐一柯。逆竖则枯。此则人孰不知。今理气倒置之急。举此无异。而人独不知。可胜叹哉。
天地间空荡荡底理。固可说也。只是外面看说。这便在人然后。方成实体。说理。舍此人字不得。
说理不如说德。在初学尤然。
先生曰。昔南雪下丈(纪济)每为主气之论。吾仰而戏告曰。长者主张气字甚力。如是则长者之子弟必好盛气凌侮驱拍人也。将以何辞禁之乎。此丈笑而不答也。(按此先生九岁十岁时语。)
通局二字。分别理气最尽。如以人心知觉言之。则知无不知。觉无不觉。理通故也。知有所不知。觉有所不觉。气局故也。
性情虽有体用之殊。才曰体用则只是一事。言理则皆理也。言气则皆气也。若以性属理。以情属气。则非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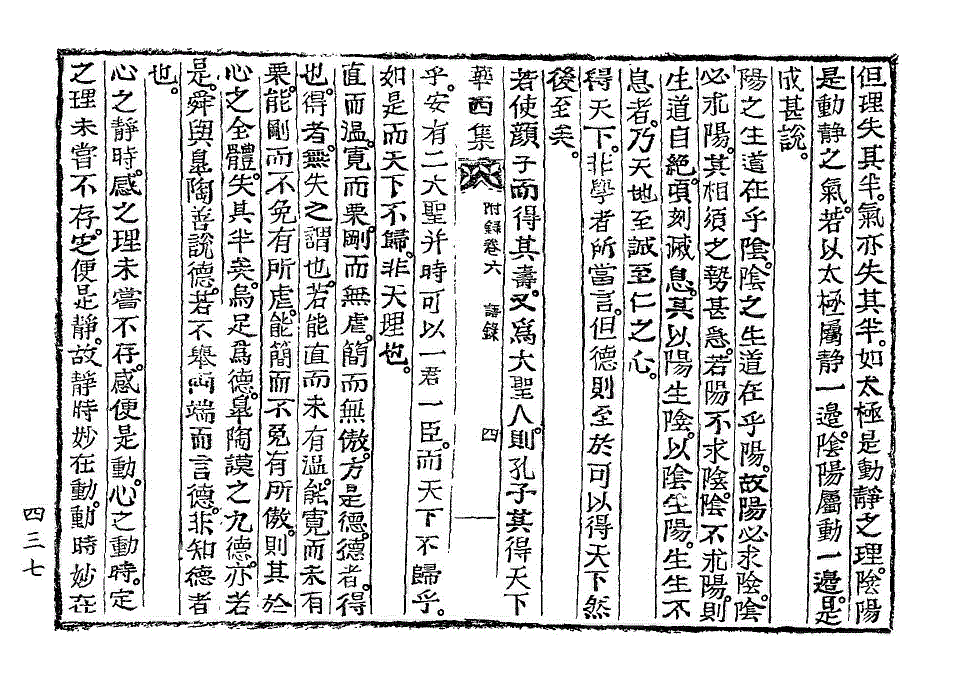 但理失其半。气亦失其半。如太极是动静之理。阴阳是动静之气。若以太极属静一边。阴阳属动一边。是成甚说。
但理失其半。气亦失其半。如太极是动静之理。阴阳是动静之气。若以太极属静一边。阴阳属动一边。是成甚说。阳之生道在乎阴。阴之生道在乎阳。故阳必求阴。阴必求阳。其相须之势甚急。若阳不求阴。阴不求阳。则生道自绝。顷刻灭息。其以阳生阴。以阴生阳。生生不息者。乃天地至诚至仁之心。
得天下。非学者所当言。但德则至于可以得天下然后至矣。
若使颜子而得其寿。又为大圣人。则孔子其得天下乎。安有二大圣并时可以一君一臣。而天下不归乎。如是而天下不归。非天理也。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方是德。德者。得也。得者。无失之谓也。若能直而未有温。能宽而未有栗。能刚而不免有所虐。能简而不免有所傲。则其于心之全体。失其半矣。乌足为德。皋陶谟之九德。亦若是。舜与皋陶善说德。若不举两端而言德。非知德者也。
心之静时。感之理未尝不存。感便是动。心之动时。定之理未尝不存。定便是静。故静时妙在动。动时妙在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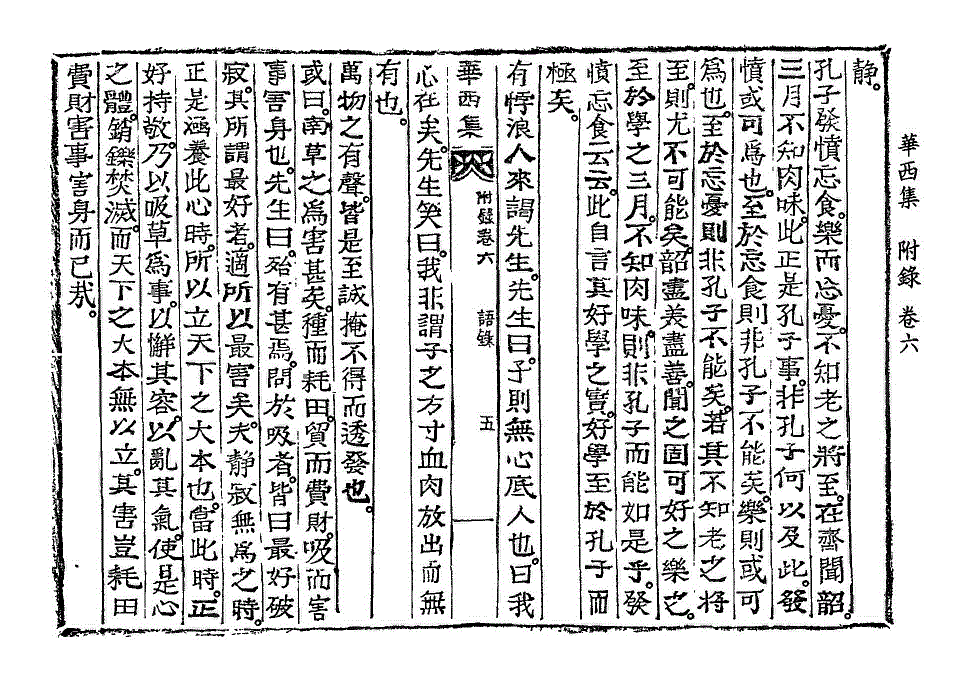 静。
静。孔子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此正是孔子事。非孔子何以及此。发愤或可为也。至于忘食则非孔子不能矣。乐则或可为也。至于忘忧则非孔子不能矣。若其不知老之将至。则尤不可能矣。韶尽美尽善。闻之固可好之乐之。至于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则非孔子而能如是乎。发愤忘食云云。此自言其好学之实。好学至于孔子而极矣。
有悖浪人来谒先生。先生曰。子则无心底人也。曰我心在矣。先生笑曰。我非谓子之方寸血肉放出而无有也。
万物之有声。皆是至诚掩不得而透发也。
或曰。南草之为害甚矣。种而耗田。贸而费财。吸而害事害身也。先生曰。殆有甚焉。问于吸者。皆曰最好破寂。其所谓最好者。适所以最害矣。夫静寂无为之时。正是涵养此心时。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当此时。正好持敬。乃以吸草为事。以懈其容。以乱其气。使是心之体。销铄焚灭。而天下之大本无以立。其害岂耗田费财害事害身而已哉。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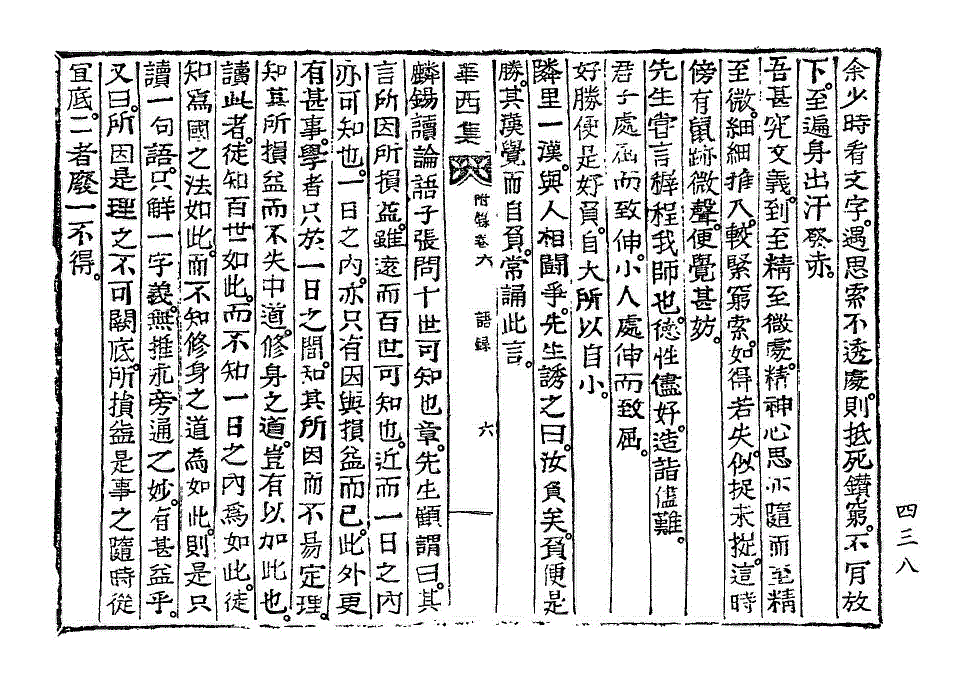 余少时看文字。遇思索不透处。则抵死钻穷。不肯放下。至遍身出汗发赤。
余少时看文字。遇思索不透处。则抵死钻穷。不肯放下。至遍身出汗发赤。吾甚究文义。到至精至微处。精神心思亦随而至精至微。细细推入。较紧穷索。如得若失。似捉未捉。这时傍有鼠迹微声。便觉甚妨。
先生尝言稚程我师也。德性尽好。造诣尽难。
君子处屈而致伸。小人处伸而致屈。
好胜便是好负。自大所以自小。
邻里一汉。与人相斗争。先生诱之曰。汝负矣。负便是胜。其汉觉而自负。常诵此言。
麟锡读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先生顾谓曰。其言所因所损益。虽远而百世可知也。近而一日之内亦可知也。一日之内。亦只有因与损益而已。此外更有甚事。学者只于一日之间。知其所因而不易定理。知其所损益而不失中道。修身之道。岂有以加此也。读此者。徒知百世如此。而不知一日之内为如此。徒知为国之法如此。而不知修身之道为如此。则是只读一句语。只解一字义。无推求旁通之妙。有甚益乎。又曰。所因是理之不可阙底。所损益是事之随时从宜底。二者废一不得。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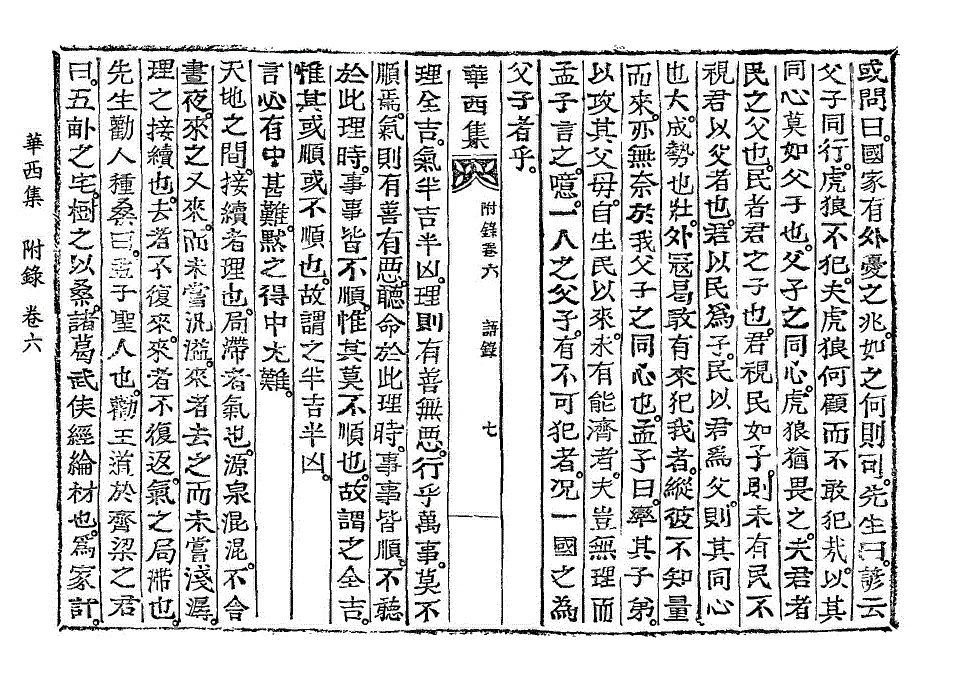 或问曰。国家有外忧之兆。如之何则可。先生曰。谚云父子同行。虎狼不犯。夫虎狼何顾而不敢犯哉。以其同心莫如父子也。父子之同心。虎狼犹畏之。夫君者民之父也。民者君之子也。君视民如子。则未有民不视君以父者也。君以民为子。民以君为父。则其同心也大。成势也壮。外寇曷敢有来犯我者。纵彼不知量而来。亦无奈于我父子之同心也。孟子曰。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夫岂无理而孟子言之。噫。一人之父子。有不可犯者。况一国之为父子者乎。
或问曰。国家有外忧之兆。如之何则可。先生曰。谚云父子同行。虎狼不犯。夫虎狼何顾而不敢犯哉。以其同心莫如父子也。父子之同心。虎狼犹畏之。夫君者民之父也。民者君之子也。君视民如子。则未有民不视君以父者也。君以民为子。民以君为父。则其同心也大。成势也壮。外寇曷敢有来犯我者。纵彼不知量而来。亦无奈于我父子之同心也。孟子曰。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夫岂无理而孟子言之。噫。一人之父子。有不可犯者。况一国之为父子者乎。理全吉。气半吉半凶。理则有善无恶。行乎万事。莫不顺焉。气则有善有恶。听命于此理时。事事皆顺。不听于此理时。事事皆不顺。惟其莫不顺也。故谓之全吉。惟其或顺或不顺也。故谓之半吉半凶。
言必有中甚难。默之得中尤难。
天地之间。接续者理也。局滞者气也。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来之又来。而未尝汎溢。来者去之而未尝浅潺。理之接续也。去者不复来。来者不复返。气之局滞也。先生劝人种桑曰。孟子圣人也。劝王道于齐梁之君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诸葛武侯经纶材也。为家计。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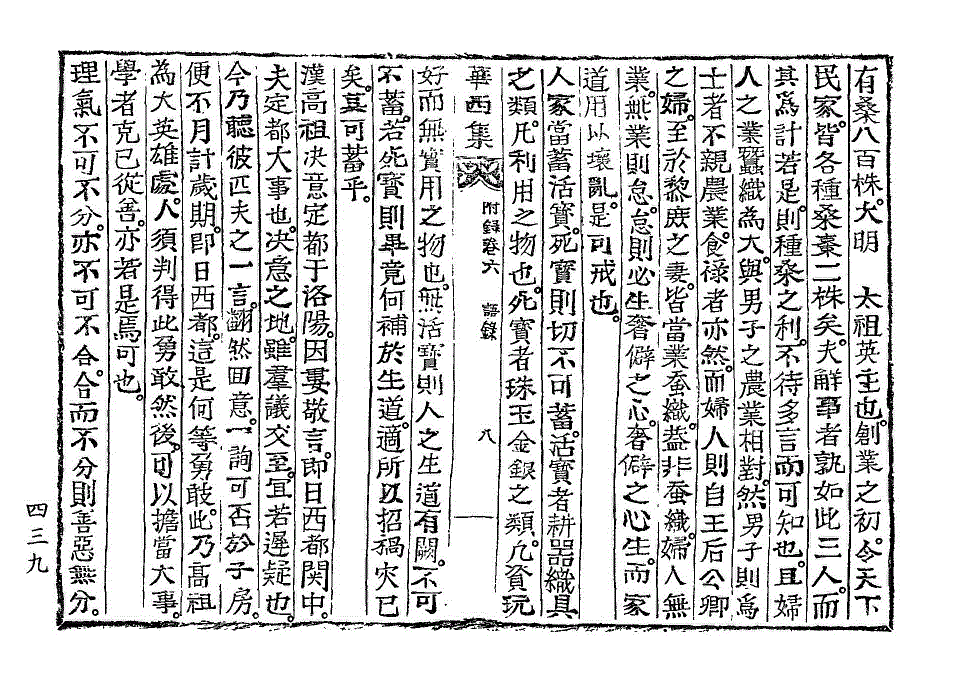 有桑八百株。大明 太祖英主也。创业之初。令天下民家。皆各种桑枣二株矣。夫解事者孰如此三人。而其为计若是。则种桑之利。不待多言而可知也。且妇人之业蚕织为大。与男子之农业相对。然男子则为士者不亲农业。食禄者亦然。而妇人则自王后公卿之妇。至于黎庶之妻。皆当业蚕织。盖非蚕织。妇人无业。无业则怠。怠则必生奢僻之心。奢僻之心生。而家道用以坏乱。是可戒也。
有桑八百株。大明 太祖英主也。创业之初。令天下民家。皆各种桑枣二株矣。夫解事者孰如此三人。而其为计若是。则种桑之利。不待多言而可知也。且妇人之业蚕织为大。与男子之农业相对。然男子则为士者不亲农业。食禄者亦然。而妇人则自王后公卿之妇。至于黎庶之妻。皆当业蚕织。盖非蚕织。妇人无业。无业则怠。怠则必生奢僻之心。奢僻之心生。而家道用以坏乱。是可戒也。人家当蓄活宝。死宝则切不可蓄。活宝者耕器织具之类。凡利用之物也。死宝者珠玉金银之类。凡资玩好而无实用之物也。无活宝则人之生道有阙。不可不蓄。若死宝则毕竟何补于生道。适所以招祸灾已矣。其可蓄乎。
汉高祖决意定都于洛阳。因娄敬言。即日西都关中。夫定都大事也。决意之地。虽群议交至。宜若迟疑也。今乃听彼匹夫之一言。翻然回意。一询可否于子房。便不月计岁期。即日西都。这是何等勇敢。此乃高祖为大英雄处。人须判得此勇敢然后。可以担当大事。学者克己从善。亦若是焉可也。
理气不可不分。亦不可不合。合而不分则善恶无分。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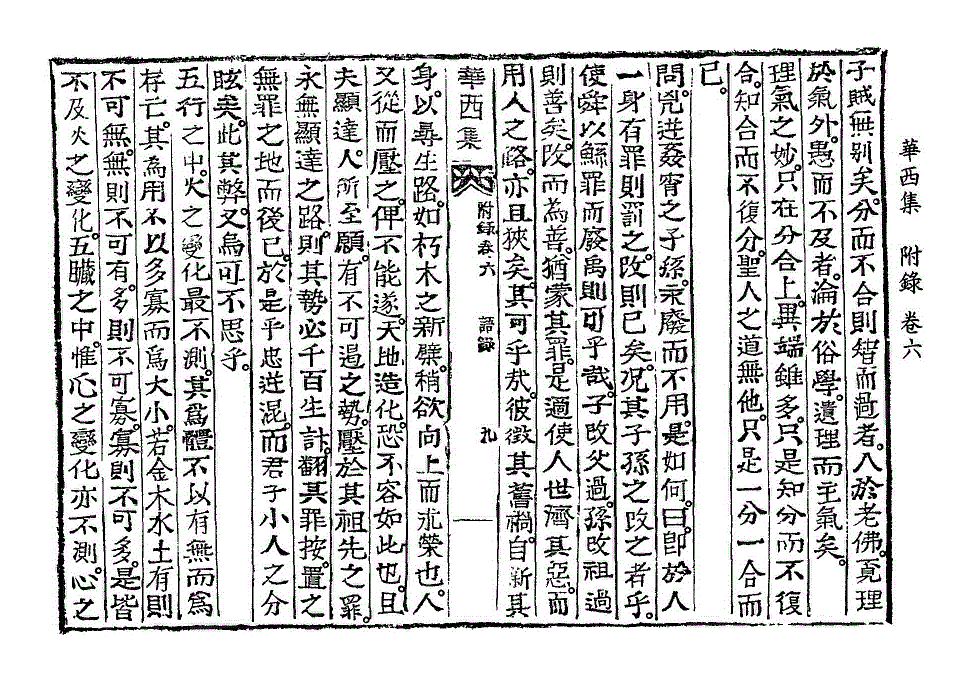 子贼无别矣。分而不合则智而过者。入于老佛。觅理于气外。愚而不及者。沦于俗学。遗理而主气矣。
子贼无别矣。分而不合则智而过者。入于老佛。觅理于气外。愚而不及者。沦于俗学。遗理而主气矣。理气之妙。只在分合上。异端虽多。只是知分而不复合。知合而不复分。圣人之道无他。只是一分一合而已。
问。凶逆奸宵之子孙。永废而不用。是如何。曰。即于人一身有罪则罚之。改则已矣。况其子孙之改之者乎。使舜以鲧罪而废禹则可乎哉。子改父过。孙改祖过则善矣。改而为善。犹蒙其罪。是适使人世济其恶。而用人之路。亦且狭矣。其可乎哉。彼徵其旧祸。自新其身。以寻生路。如朽木之新檗。稍欲向上而求荣也。人又从而压之。俾不能遂。天地造化。恐不容如此也。且夫显达。人所至愿。有不可遏之势。压于其祖先之罪。永无显达之路。则其势必千百生计。翻其罪按。置之无罪之地而后已。于是乎忠逆混。而君子小人之分眩矣。此其弊。又乌可不思乎。
五行之中。火之变化最不测。其为体不以有无而为存亡。其为用不以多寡而为大小。若金木水土有则不可无。无则不可有。多则不可寡。寡则不可多。是皆不及火之变化。五脏之中。惟心之变化亦不测。心之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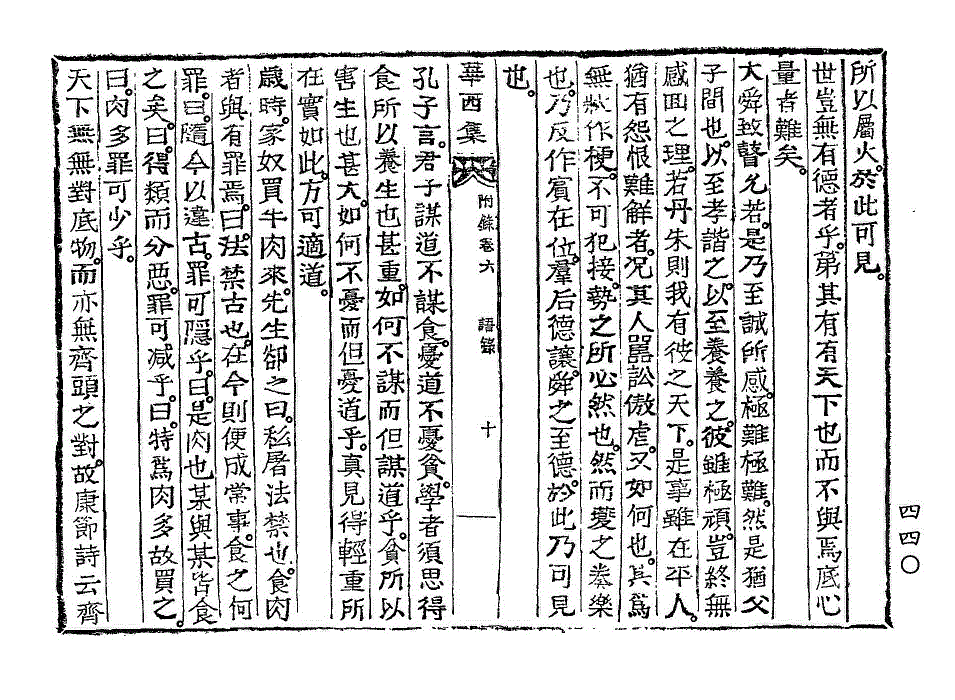 所以属火。于此可见。
所以属火。于此可见。世岂无有德者乎。第其有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底心量者难矣。
大舜致瞽允若。是乃至诚所感。极难极难。然是犹父子间也。以至孝谐之。以至养养之。彼虽极顽。岂终无感回之理。若丹朱则我有彼之天下。是事虽在平人。犹有怨恨难解者。况其人嚚讼傲虐。又如何也。其为无状作梗。不可犯接。势之所必然也。然而夔之奏乐也。乃反作宾在位。群后德让。舜之至德。于此乃可见也。
孔子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学者须思得食所以养生也甚重。如何不谋而但谋道乎。贫所以害生也甚大。如何不忧而但忧道乎。真见得轻重所在实如此。方可适道。
岁时。家奴买牛肉来。先生却之曰。私屠法禁也。食肉者与有罪焉。曰。法禁古也。在今则便成常事。食之何罪。曰。随今以违古。罪可隐乎。曰。是肉也某与某皆食之矣。曰。得类而分恶。罪可减乎。曰。特为肉多故买之。曰。肉多罪可少乎。
天下无无对底物。而亦无齐头之对。故康节诗云齐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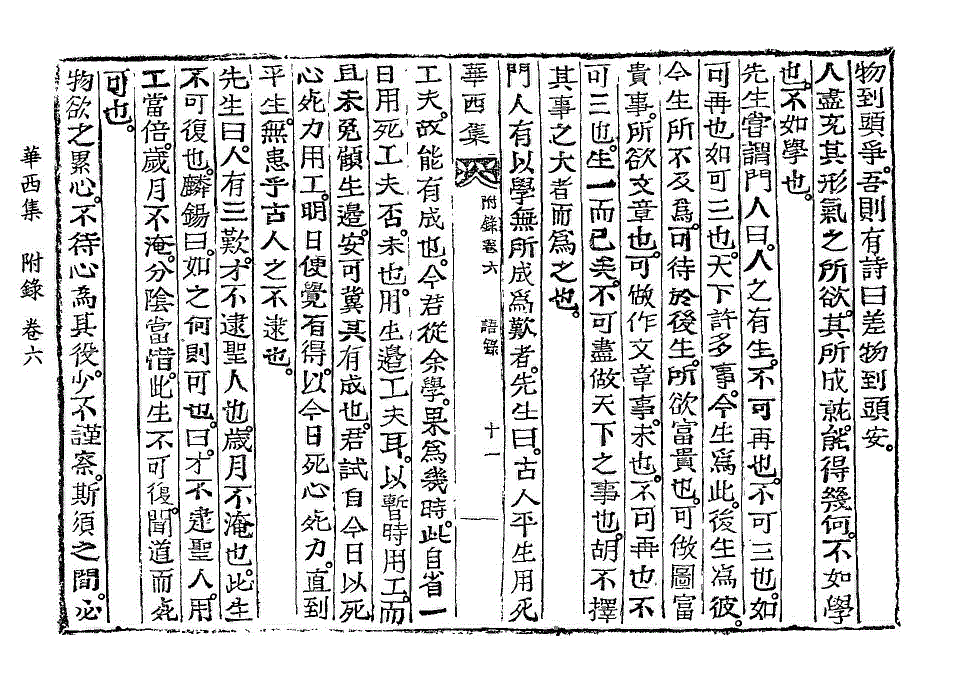 物到头争。吾则有诗曰差物到头安。
物到头争。吾则有诗曰差物到头安。人尽充其形气之所欲。其所成就。能得几何。不如学也。不如学也。
先生尝谓门人曰。人之有生。不可再也。不可三也。如可再也如可三也。天下许多事。今生为此。后生为彼。今生所不及为。可待于后生。所欲富贵也。可做图富贵事。所欲文章也。可做作文章事。未也。不可再也不可三也。生一而已矣。不可尽做天下之事也。胡不择其事之大者而为之也。
门人有以学无所成为叹者。先生曰。古人平生用死工夫。故能有成也。今君从余学。果为几时。此自省一日用死工夫否。未也。用生边工夫耳。以暂时用工。而且未免顾生边。安可冀其有成也。君试自今日以死心死力用工。明日便觉有得。以今日死心死力。直到平生。无患乎古人之不逮也。
先生曰。人有三叹。才不逮圣人也。岁月不淹也。此生不可复也。麟锡曰。如之何则可也。曰。才不逮圣人。用工当倍。岁月不淹。分阴当惜。此生不可复。闻道而死可也。
物欲之累心。不待心为其役。少不谨察。斯须之间。必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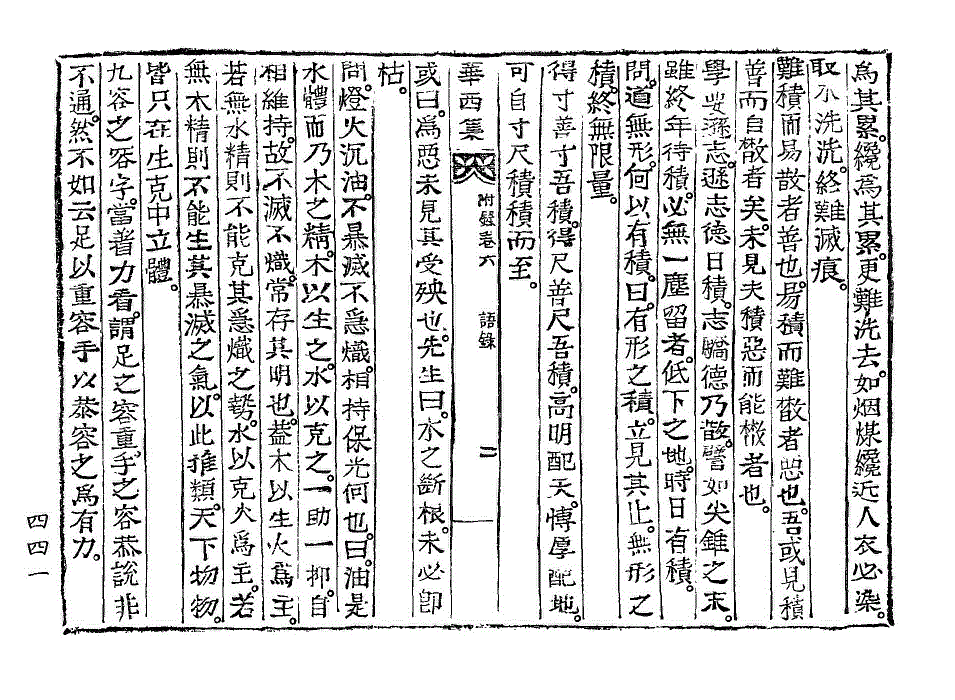 为其累。才为其累。更难洗去。如烟煤才近人衣必染。取水洗洗。终难灭痕。
为其累。才为其累。更难洗去。如烟煤才近人衣必染。取水洗洗。终难灭痕。难积而易散者善也。易积而难散者恶也。吾或见积善而自散者矣。未见夫积恶而能散者也。
学要逊志。逊志德日积。志骄德乃散。譬如尖锥之末。虽终年待积。必无一尘留者。低下之地。时日有积。
问。道无形。何以有积。曰。有形之积。立见其止。无形之积。终无限量。
得寸善寸吾积。得尺善尺吾积。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可自寸尺积积而至。
或曰。为恶未见其受殃也。先生曰。木之断根。未必即枯。
问。灯火沉油。不暴灭不急炽。相持保光何也。曰。油是水体而乃木之精。木以生之。水以克之。一助一抑。自相维持。故不灭不炽。常存其明也。盖木以生火为主。若无水精则不能克其急炽之势。水以克火为主。若无木精则不能生其暴灭之气。以此推类。天下物物。皆只在生克中立体。
九容之容字。当着力看。谓足之容重。手之容恭说非不通。然不如云足以重容手以恭容之为有力。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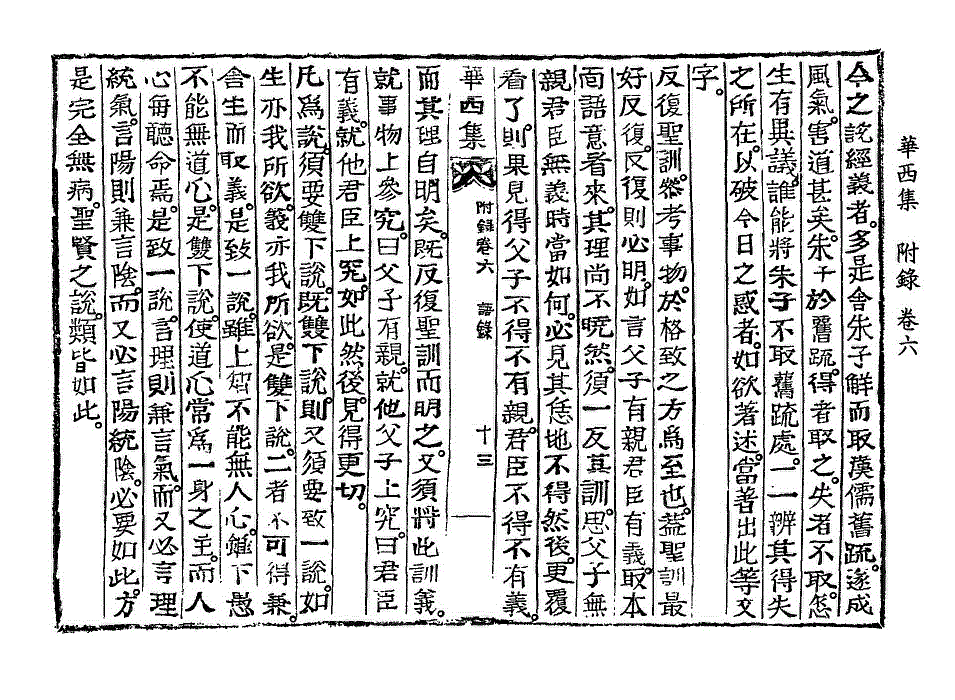 今之说经义者。多是舍朱子解而取汉儒旧疏。遂成风气。害道甚矣。朱子于旧疏。得者取之。失者不取。怎生有异议。谁能将朱子不取旧疏处。一一辨其得失之所在。以破今日之惑者。如欲著述。当著出此等文字。
今之说经义者。多是舍朱子解而取汉儒旧疏。遂成风气。害道甚矣。朱子于旧疏。得者取之。失者不取。怎生有异议。谁能将朱子不取旧疏处。一一辨其得失之所在。以破今日之惑者。如欲著述。当著出此等文字。反复圣训。参考事物。于格致之方为至也。盖圣训最好反复。反复则必明。如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取本面语意看来。其理尚不晓然。须一反其训。思父子无亲君臣无义时当如何。必见其恁地不得然后。更覆看了。则果见得父子不得不有亲。君臣不得不有义。而其理自明矣。既反复圣训而明之。又须将此训义。就事物上参究。曰父子有亲。就他父子上究。曰君臣有义。就他君臣上究。如此然后。见得更切。
凡为说。须要双下说。既双下说。则又须要致一说。如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是双下说。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是致一说。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是双下说。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是致一说。言理则兼言气。而又必言理统气。言阳则兼言阴。而又必言阳统阴。必要如此。方是完全无病。圣贤之说。类皆如此。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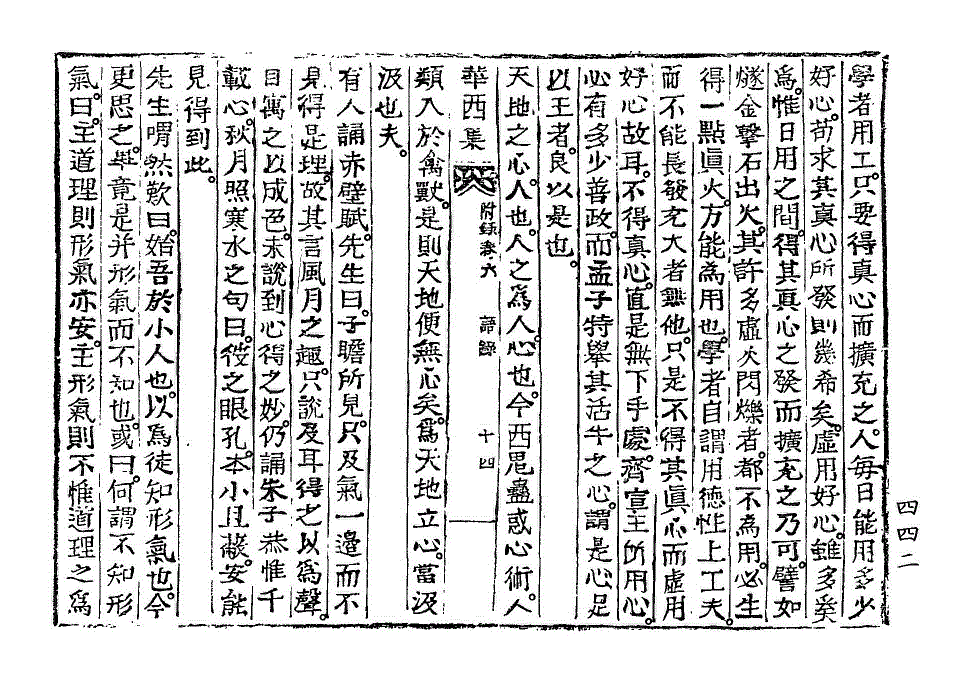 学者用工。只要得真心而扩充之。人每日能用多少好心。苟求其真心所发则几希矣。虚用好心。虽多奚为。惟日用之间。得其真心之发而扩充之乃可。譬如燧金击石出火。其许多虚火闪烁者。都不为用。必生得一点真火。方能为用也。学者自谓用德性上工夫。而不能长发充大者无他。只是不得其真心而虚用好心故耳。不得真心。直是无下手处。齐宣王所用心。必有多少善政。而孟子特举其活牛之心。谓是心足以王者。良以是也。
学者用工。只要得真心而扩充之。人每日能用多少好心。苟求其真心所发则几希矣。虚用好心。虽多奚为。惟日用之间。得其真心之发而扩充之乃可。譬如燧金击石出火。其许多虚火闪烁者。都不为用。必生得一点真火。方能为用也。学者自谓用德性上工夫。而不能长发充大者无他。只是不得其真心而虚用好心故耳。不得真心。直是无下手处。齐宣王所用心。必有多少善政。而孟子特举其活牛之心。谓是心足以王者。良以是也。天地之心。人也。人之为人。心也。今西鬼蛊惑心术。人类入于禽兽。是则天地便无心矣。为天地立心。当汲汲也夫。
有人诵赤壁赋。先生曰。子瞻所见。只及气一边而不见得是理。故其言风月之趣。只说及耳得之以为声。目寓之以成色。未说到心得之妙。仍诵朱子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之句曰。彼之眼孔。本小且蔽。安能见得到此。
先生喟然叹曰。始吾于小人也。以为徒知形气也。今更思之。毕竟是并形气而不知也。或曰。何谓不知形气。曰。主道理则形气亦安。主形气则不惟道理之为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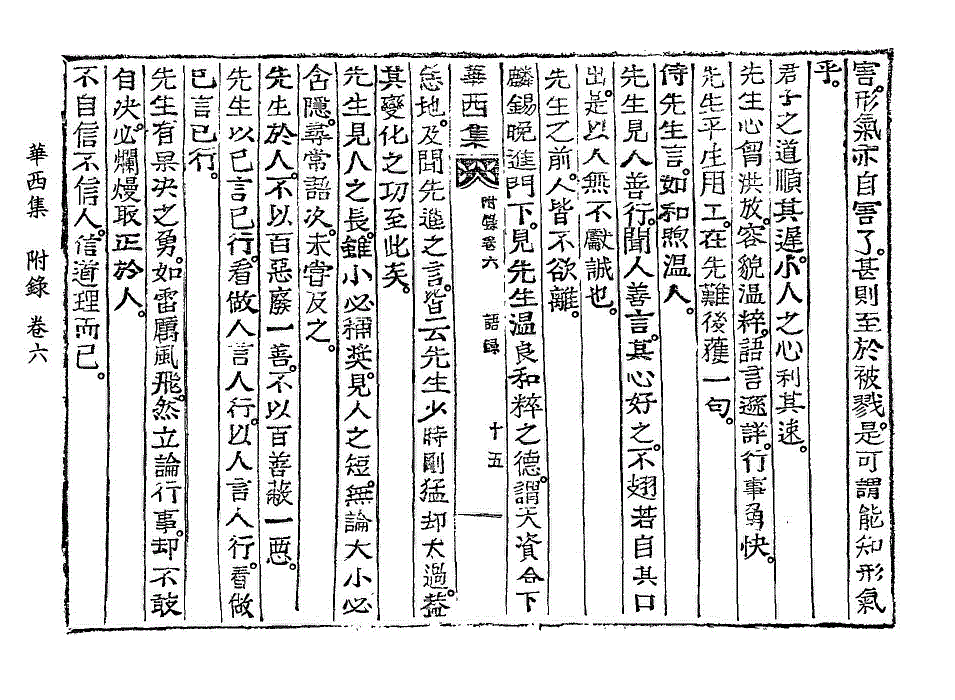 害。形气亦自害了。甚则至于被戮。是可谓能知形气乎。
害。形气亦自害了。甚则至于被戮。是可谓能知形气乎。君子之道顺其迟。小人之心利其速。
先生心胸洪放。容貌温粹。语言逊详。行事勇快。
先生平生用工。在先难后获一句。
侍先生言。如和煦温人。
先生见人善行。闻人善言。其心好之。不翅若自其口出。是以人无不献诚也。
先生之前。人皆不欲离。
麟锡晚进门下。见先生温良和粹之德。谓天资合下恁地。及闻先进之言。皆云先生少时刚猛却太过。盖其变化之功至此矣。
先生见人之长。虽小必称奖。见人之短。无论大小必含隐。寻常语次。未尝及之。
先生于人。不以百恶废一善。不以百善蔽一恶。
先生以己言己行。看做人言人行。以人言人行。看做己言己行。
先生有果决之勇。如雷厉风飞。然立论行事。却不敢自决。必烂熳取正于人。
不自信不信人。信道理而已。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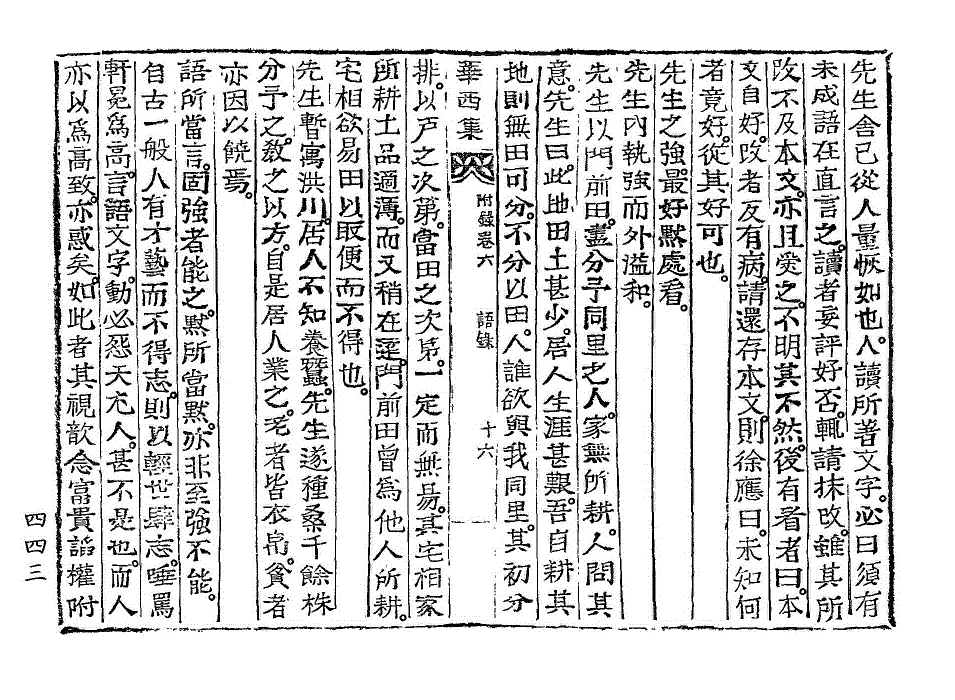 先生舍己从人量恢如也。人读所著文字。必曰须有未成语在直言之。读者妄评好否。辄请抹改。虽其所改不及本文。亦且受之。不明其不然。后有看者曰。本文自好。改者反有病。请还存本文。则徐应曰。未知何者竟好。从其好可也。
先生舍己从人量恢如也。人读所著文字。必曰须有未成语在直言之。读者妄评好否。辄请抹改。虽其所改不及本文。亦且受之。不明其不然。后有看者曰。本文自好。改者反有病。请还存本文。则徐应曰。未知何者竟好。从其好可也。先生之强。最好默处看。
先生内执强而外溢和。
先生以门前田。尽分予同里之人。家无所耕。人问其意。先生曰。此地田土甚少。居人生涯甚艰。吾自耕其地则无田可分。不分以田。人谁欲与我同里。其初分排。以户之次第。当田之次第。一定而无易。其宅相家所耕土品适薄。而又稍在远。门前田曾为他人所耕。宅相欲易田以取便而不得也。
先生暂寓洪川。居人不知养蚕。先生遂种桑千馀株分予之。教之以方。自是居人业之。老者皆衣帛。贫者亦因以饶焉。
语所当言。固强者能之。默所当默。亦非至强不能。
自古一般人有才艺而不得志。则以轻世肆志。唾骂轩冕为高。言语文字。动必怨天尤人。甚不是也。而人亦以为高致。亦惑矣。如此者其视歆念富贵谄权附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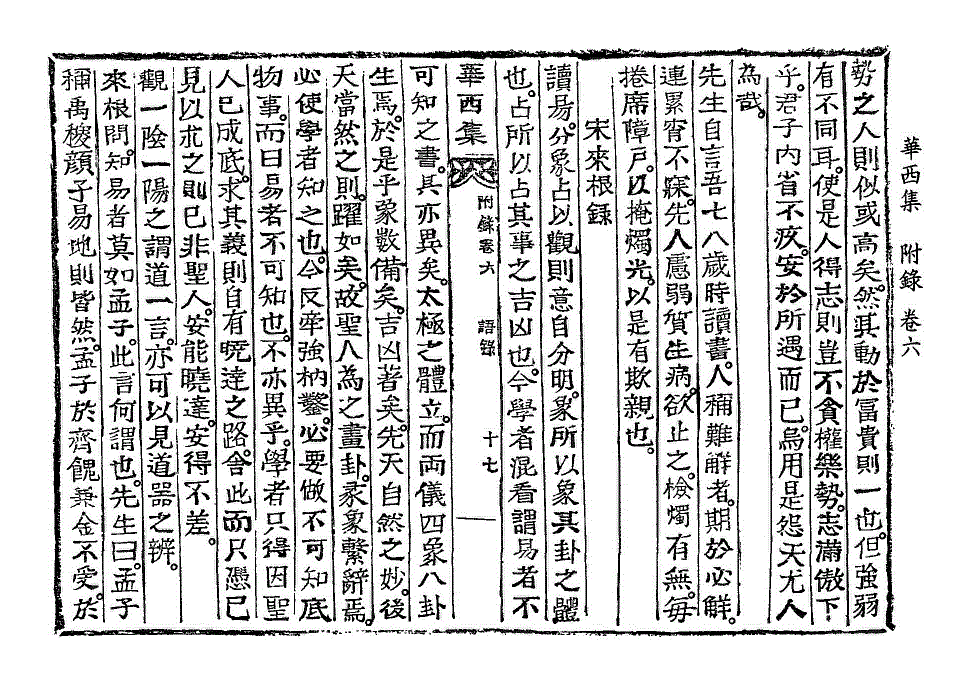 势之人则似或高矣。然其动于富贵则一也。但强弱有不同耳。使是人得志则岂不贪权乐势。志满傲下乎。君子内省不疚。安于所遇而已。乌用是怨天尤人为哉。
势之人则似或高矣。然其动于富贵则一也。但强弱有不同耳。使是人得志则岂不贪权乐势。志满傲下乎。君子内省不疚。安于所遇而已。乌用是怨天尤人为哉。先生自言吾七八岁时读书。人称难解者。期于必解。连累宵不寐。先人虑弱质生病。欲止之。检烛有无。每捲席障户。以掩烛光。以是有欺亲也。
宋来根录
读易。分象占以观则意自分明。象所以象其卦之体也。占所以占其事之吉凶也。今学者混看谓易者不可知之书。其亦异矣。太极之体立。而两仪四象八卦生焉。于是乎象数备矣。吉凶著矣。先天自然之妙。后天当然之则。跃如矣。故圣人为之画卦。彖象系辞焉。必使学者知之也。今反牵强枘凿。必要做不可知底物事。而曰易者不可知也。不亦异乎。学者只得因圣人已成底。求其义则自有晓达之路。舍此而只凭己见以求之则己非圣人。安能晓达。安得不差。
观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言。亦可以见道器之辨。
来根问。知易者莫如孟子。此言何谓也。先生曰。孟子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于齐馈兼金不受。于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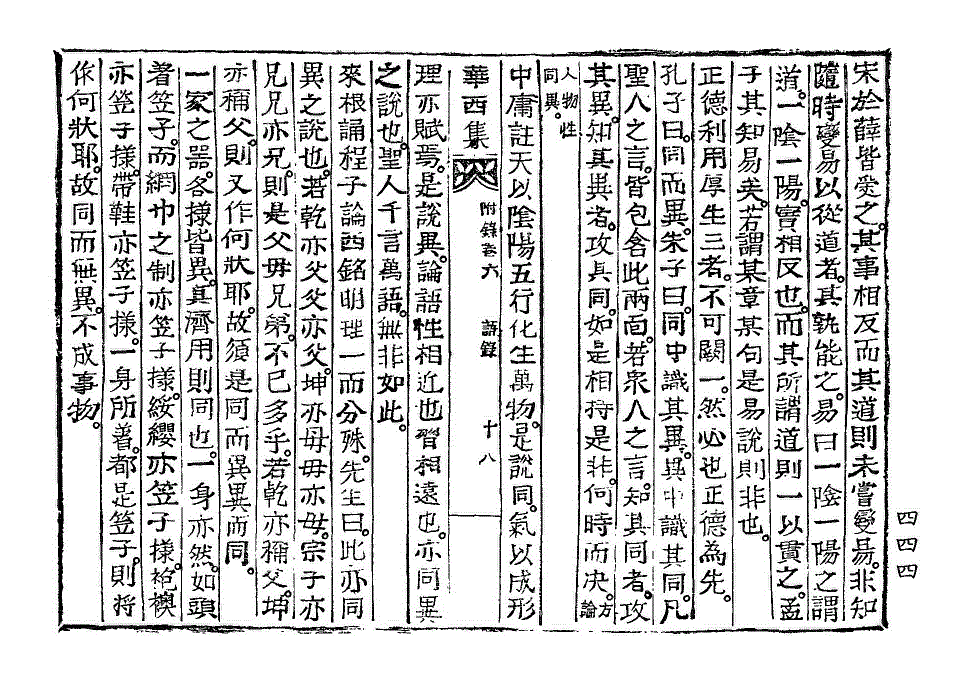 宋于薛皆受之。其事相反而其道则未尝变易。非知随时变易以从道者。其孰能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实相反也。而其所谓道则一以贯之。孟子其知易矣。若谓某章某句是易说则非也。
宋于薛皆受之。其事相反而其道则未尝变易。非知随时变易以从道者。其孰能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实相反也。而其所谓道则一以贯之。孟子其知易矣。若谓某章某句是易说则非也。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不可阙一。然必也正德为先。
孔子曰。同而异。朱子曰。同中识其异。异中识其同。凡圣人之言。皆包含此两面。若众人之言。知其同者。攻其异。知其异者。攻其同。如是相持是非。何时而决。(方论人物性同异。)
中庸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是说同。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说异。论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亦同异之说也。圣人千言万语。无非如此。
来根诵程子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先生曰。此亦同异之说也。若乾亦父父亦父。坤亦母母亦母。宗子亦兄兄亦兄。则是父母兄弟。不已多乎。若乾亦称父。坤亦称父。则又作何状耶。故须是同而异异而同。
一家之器。各㨾皆异。其济用则同也。一身亦然。如头着笠子。而网巾之制亦笠子㨾。绥缨亦笠子㨾。袍袄亦笠子㨾。带鞋亦笠子㨾。一身所着。都是笠子。则将作何状耶。故同而无异。不成事物。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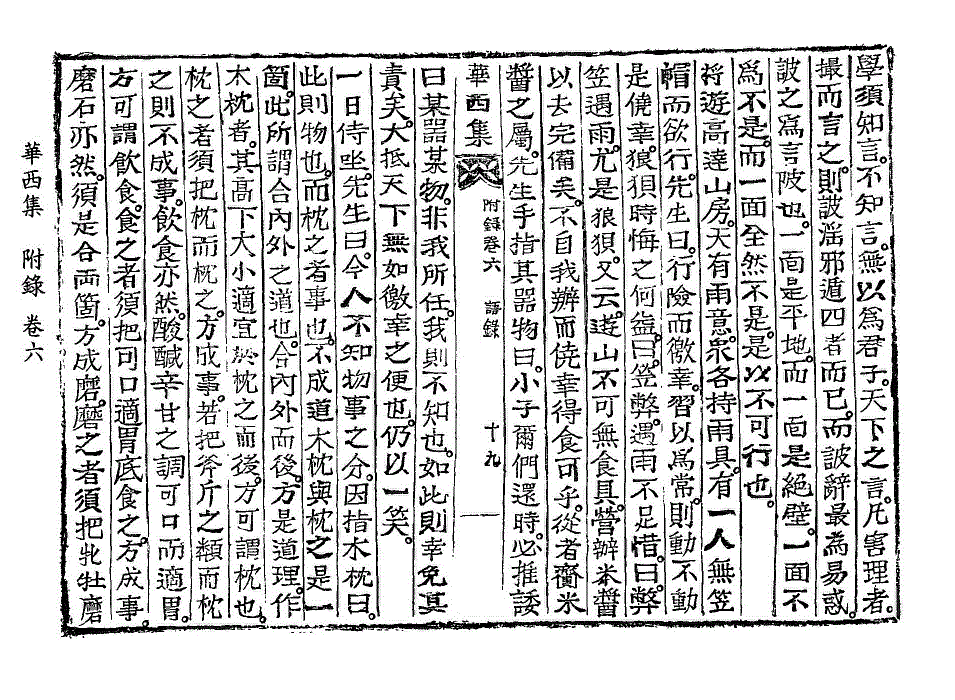 学须知言。不知言。无以为君子。天下之言。凡害理者。撮而言之。则诐淫邪遁四者而已。而诐辞最为易惑。诐之为言陂也。一面是平地。而一面是绝壁。一面不为不是。而一面全然不是。是以不可行也。
学须知言。不知言。无以为君子。天下之言。凡害理者。撮而言之。则诐淫邪遁四者而已。而诐辞最为易惑。诐之为言陂也。一面是平地。而一面是绝壁。一面不为不是。而一面全然不是。是以不可行也。将游高达山房。天有雨意。众各持雨具。有一人无笠帽而欲行。先生曰。行险而徼幸。习以为常。则动不动是侥幸。狼狈时悔之何益。曰。笠弊。遇雨不足惜。曰。弊笠遇雨。尤是狼狈。又云。游山不可无食具。营办米酱以去完备矣。不自我办而侥幸得食可乎。从者赍米酱之属。先生手指其器物曰。小子尔们还时。必推诿曰某器某物。非我所任。我则不知也。如此则幸免其责矣。大抵天下无如徼幸之便也。仍以一笑。
一日侍坐。先生曰。今人不知物事之分。因指木枕曰。此则物也。而枕之者事也。不成道木枕与枕之是一个。此所谓合内外之道也。合内外而后。方是道理。作木枕者。其高下大小适宜于枕之而后。方可谓枕也。枕之者须把枕而枕之。方成事。若把斧斤之类而枕之则不成事。饮食亦然。酸咸辛甘之调可口而适胃。方可谓饮食。食之者须把可口适胃底食之。方成事。磨石亦然。须是合两个。方成磨。磨之者须把牝牡磨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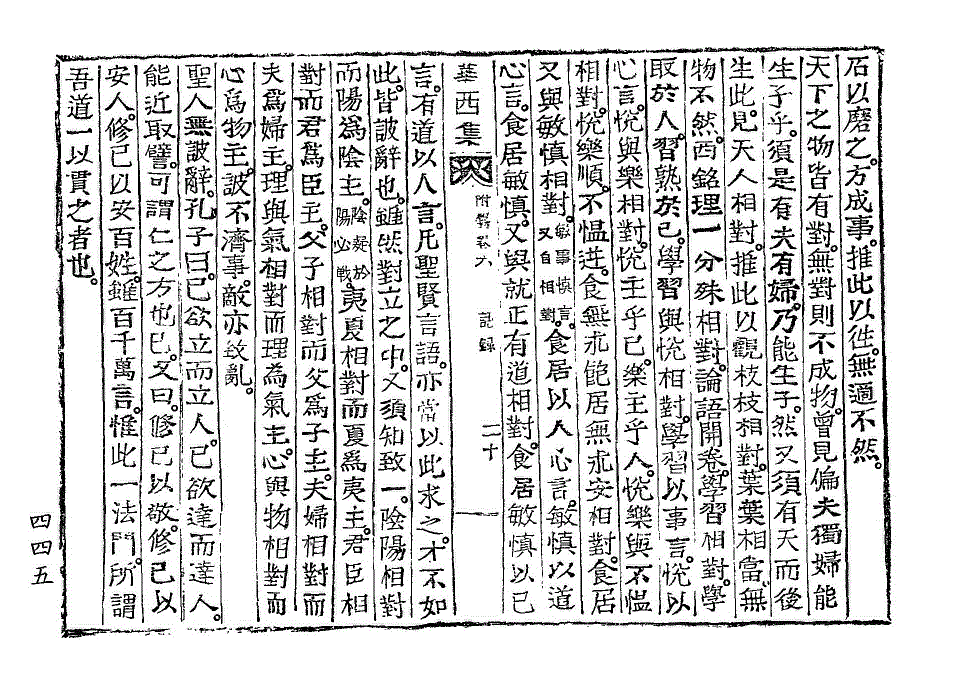 石以磨之。方成事。推此以往。无适不然。
石以磨之。方成事。推此以往。无适不然。天下之物皆有对。无对则不成物。曾见偏夫独妇能生子乎。须是有夫有妇。乃能生子。然又须有天而后生此。见天人相对。推此以观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无物不然。西铭理一分殊相对。论语开卷。学习相对。学取于人。习熟于己。学习与悦相对。学习以事言。悦以心言。悦与乐相对。悦主乎己。乐主乎人。悦乐与不愠相对。悦乐顺。不愠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相对。食居又与敏慎相对。(敏事慎言。又自相对。)食居以人心言。敏慎以道心言。食居敏慎。又与就正有道相对。食居敏慎以己言。有道以人言。凡圣贤言语。亦当以此求之。才不如此。皆诐辞也。虽然对立之中。又须知致一。阴阳相对而阳为阴主。(阴疑于阳必战。)夷夏相对而夏为夷主。君臣相对而君为臣主。父子相对而父为子主。夫妇相对而夫为妇主。理与气相对而理为气主。心与物相对而心为物主。诐不济事。敌亦致乱。
圣人无诐辞。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又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虽百千万言。惟此一法门。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者也。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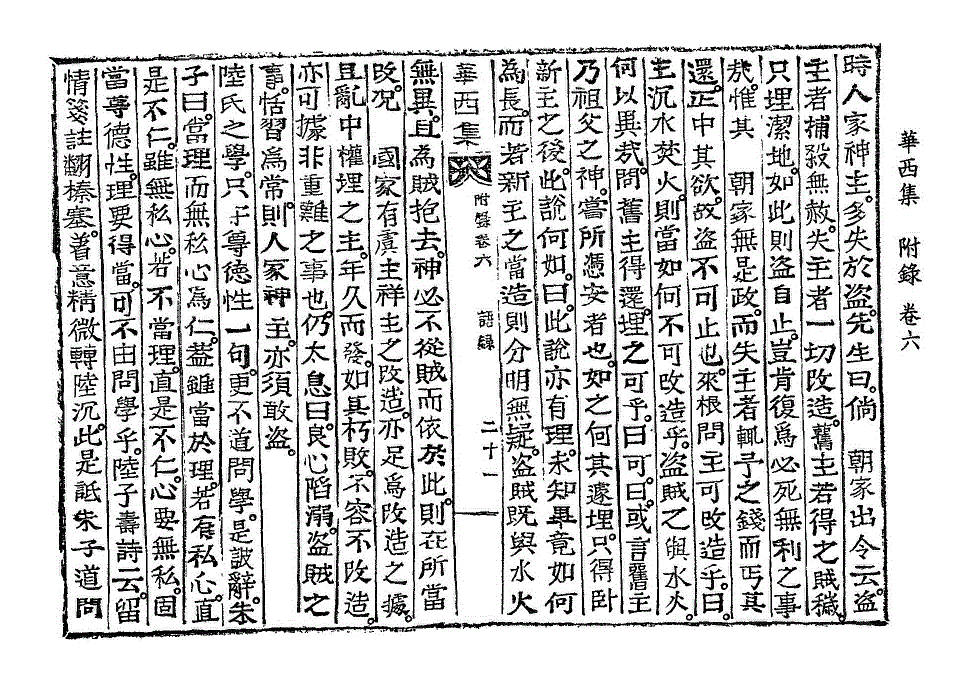 时人家神主。多失于盗。先生曰。倘 朝家出令云。盗主者捕杀无赦。失主者一切改造。旧主若得之贼秽。只埋洁地。如此则盗自止。岂肯复为必死无利之事哉。惟其 朝家无是政。而失主者辄予之钱而丐其还。正中其欲。故盗不可止也。来根问主可改造乎。曰。主沉水焚火。则当如何不可改造乎。盗贼之与水火。何以异哉。问旧主得还。埋之可乎。曰可。曰。或言旧主乃祖父之神。尝所凭安者也。如之何其遽埋。只得卧新主之后。此说何如。曰。此说亦有理。未知毕竟如何为长。而若新主之当造则分明无疑。盗贼既与水火无异。且为贼抱去。神必不从贼而依于此。则在所当改。况 国家有虞主祥主之改造。亦足为改造之据。且乱中权埋之主。年久而发。如其朽败。不容不改造。亦可据非重难之事也。仍太息曰。良心陷溺。盗贼之事。恬习为常。则人家神主。亦须敢盗。
时人家神主。多失于盗。先生曰。倘 朝家出令云。盗主者捕杀无赦。失主者一切改造。旧主若得之贼秽。只埋洁地。如此则盗自止。岂肯复为必死无利之事哉。惟其 朝家无是政。而失主者辄予之钱而丐其还。正中其欲。故盗不可止也。来根问主可改造乎。曰。主沉水焚火。则当如何不可改造乎。盗贼之与水火。何以异哉。问旧主得还。埋之可乎。曰可。曰。或言旧主乃祖父之神。尝所凭安者也。如之何其遽埋。只得卧新主之后。此说何如。曰。此说亦有理。未知毕竟如何为长。而若新主之当造则分明无疑。盗贼既与水火无异。且为贼抱去。神必不从贼而依于此。则在所当改。况 国家有虞主祥主之改造。亦足为改造之据。且乱中权埋之主。年久而发。如其朽败。不容不改造。亦可据非重难之事也。仍太息曰。良心陷溺。盗贼之事。恬习为常。则人家神主。亦须敢盗。陆氏之学。只守尊德性一句。更不道问学。是诐辞。朱子曰。当理而无私心为仁。盖虽当于理。若有私心。直是不仁。虽无私心。若不当理。直是不仁。心要无私。固当尊德性。理要得当。可不由问学乎。陆子寿诗云。留情笺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此是诋朱子道问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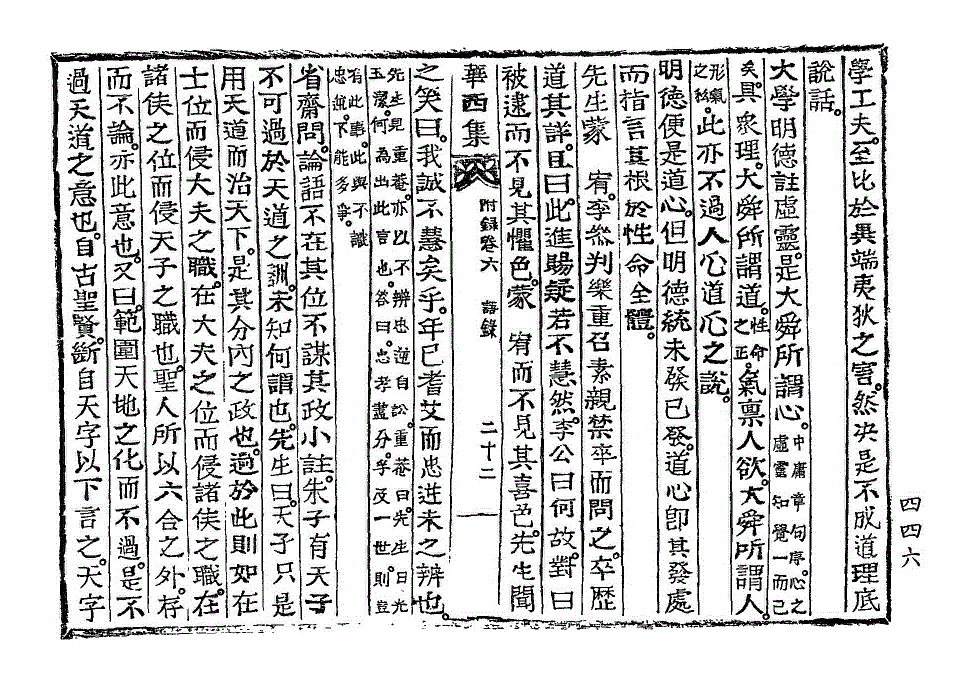 学工夫。至比于异端夷狄之害。然决是不成道理底说话。
学工夫。至比于异端夷狄之害。然决是不成道理底说话。大学明德注虚灵。是大舜所谓心。(中庸章句序。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具众理。大舜所谓道。(性命之正。)气禀人欲。大舜所谓人。(形气之私。)此亦不过人心道心之说。
明德便是道心。但明德统未发已发。道心即其发处而指言其根于性命全体。
先生蒙 宥。李参判乐重召素亲禁卒而问之。卒历道其详。且曰。此进赐疑若不慧然。李公曰何故。对曰被逮而不见其惧色。蒙 宥而不见其喜色。先生闻之笑曰。我诚不慧矣乎。年已耆艾而忠逆未之辨也。(先生见重庵。亦以不辨忠逆自讼。重庵曰。先生日光玉洁。何为出此言也。答曰。忠孝尽分。孚及一世。则岂有此事。此与不识忠逆。不能多争。)
省斋问。论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小注。朱子有天子不可过于天道之训。未知何谓也。先生曰。天子只是用天道而治天下。是其分内之政也。过于此则如在士位而侵大夫之职。在大夫之位而侵诸侯之职。在诸侯之位而侵天子之职也。圣人所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亦此意也。又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是不过天道之意也。自古圣贤。断自天字以下言之。天字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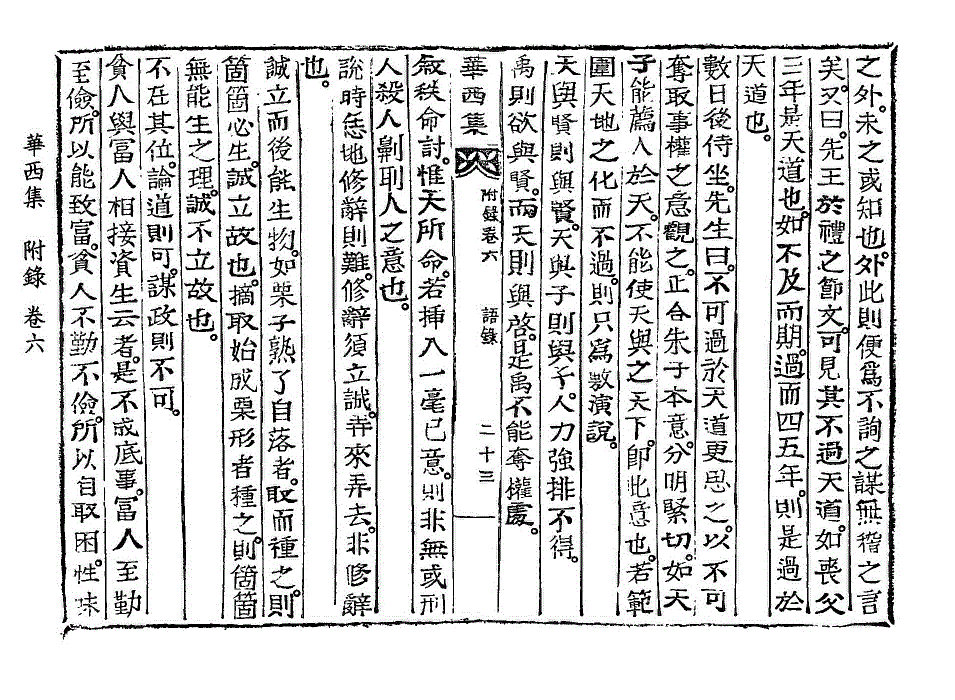 之外。未之或知也。外此则便为不询之谋无稽之言矣。又曰。先王于礼之节文。可见其不过天道。如丧父三年是天道也。如不及而期。过而四五年。则是过于天道也。
之外。未之或知也。外此则便为不询之谋无稽之言矣。又曰。先王于礼之节文。可见其不过天道。如丧父三年是天道也。如不及而期。过而四五年。则是过于天道也。数日后侍坐。先生曰。不可过于天道更思之。以不可夺取事权之意观之。正合朱子本意。分明紧切。如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即此意也。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则只为敷演说。
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人力强排不得。
禹则欲与贤。而天则与启。是禹不能夺权处。
叙秩命讨。惟天所命。若插入一毫己意。则非无或刑人杀人劓刵人之意也。
说时恁地修辞则难。修辞须立诚。弄来弄去。非修辞也。
诚立而后能生物。如栗子熟了自落者。取而种之。则个个必生。诚立故也。摘取始成栗形者种之。则个个无能生之理。诚不立故也。
不在其位。论道则可。谋政则不可。
贫人与富人相接资生云者。是不成底事。富人至勤至俭。所以能致富。贫人不勤不俭。所以自取困。性味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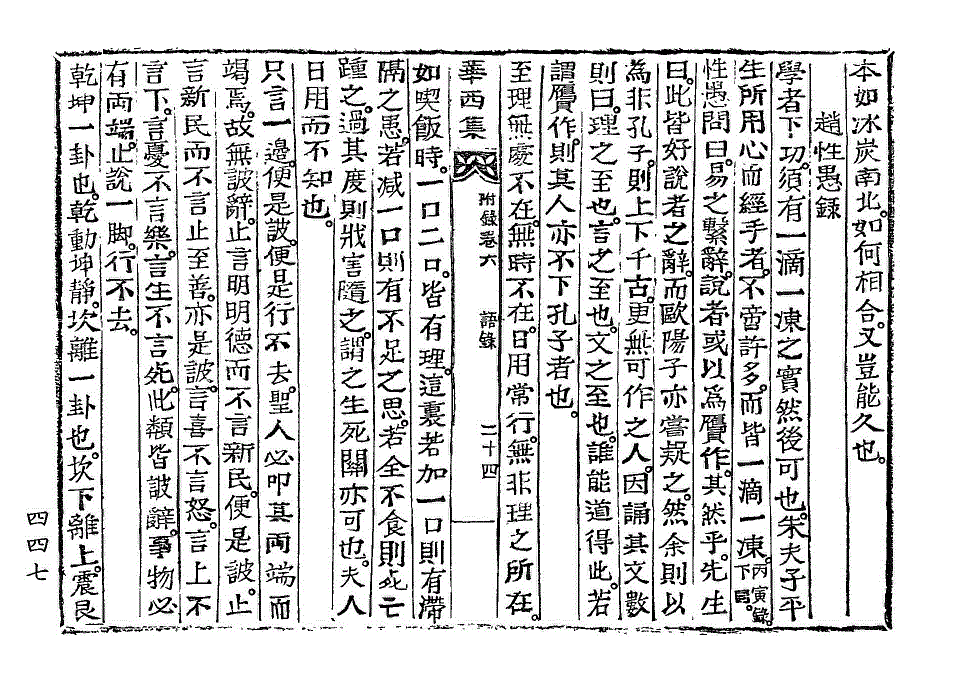 本如冰炭南北。如何相合。又岂能久也。
本如冰炭南北。如何相合。又岂能久也。赵性愚录
学者下功。须有一滴一冻之实然后可也。朱夫子平生所用心而经手者。不啻许多。而皆一滴一冻。(丙寅录。下同。)
性愚问曰。易之系辞。说者或以为赝作。其然乎。先生曰。此皆好说者之辞。而欧阳子亦尝疑之。然余则以为非孔子。则上下千古。更无可作之人。因诵其文数则曰。理之至也。言之至也。文之至也。谁能道得此。若谓赝作。则其人亦不下孔子者也。
至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日用常行。无非理之所在。如吃饭时。一口二口。皆有理。这里若加一口则有滞隔之患。若减一口则有不足之思。若全不食则死亡踵之。过其度则戕害随之。谓之生死关亦可也。夫人日用而不知也。
只言一边。便是诐。便是行不去。圣人必叩其两端而竭焉。故无诐辞。止言明明德而不言新民。便是诐。止言新民而不言止至善。亦是诐。言喜不言怒。言上不言下。言忧不言乐。言生不言死。此类皆诐辞。事物必有两端。止说一脚。行不去。
乾坤一卦也。乾动坤静。坎离一卦也。坎下离上。震艮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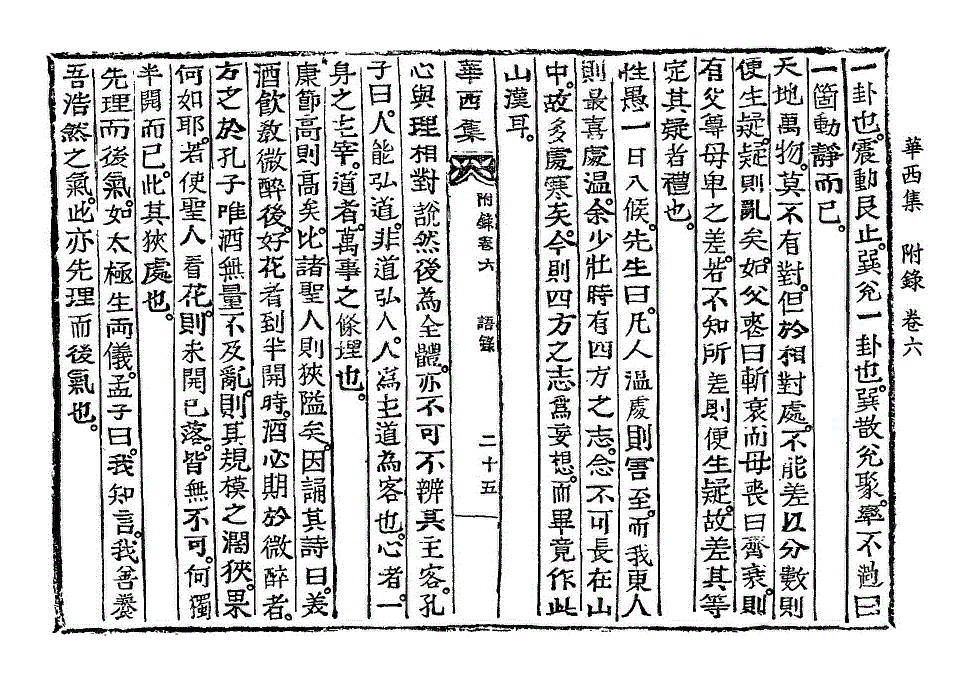 一卦也。震动艮止。巽兑一卦也。巽散兑聚。率不过曰一个动静而已。
一卦也。震动艮止。巽兑一卦也。巽散兑聚。率不过曰一个动静而已。天地万物。莫不有对。但于相对处。不能差以分数则便生疑。疑则乱矣。如父丧曰斩衰而母丧曰齐衰。则有父尊母卑之差。若不知所差则便生疑。故差其等定其疑者礼也。
性愚一日入候。先生曰。凡人温处则害至。而我东人则最喜处温。余少壮时有四方之志。念不可长在山中。故多处寒矣。今则四方之志为妄想。而毕竟作此山汉耳。
心与理相对说然后为全体。亦不可不辨其主客。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为主道为客也。心者。一身之主宰。道者。万事之条理也。
康节高则高矣。比诸圣人则狭隘矣。因诵其诗曰。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酒必期于微醉者。方之于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则其规模之阔狭。果何如耶。若使圣人看花。则未开已落。皆无不可。何独半开而已。此其狭处也。
先理而后气。如太极生两仪。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亦先理而后气也。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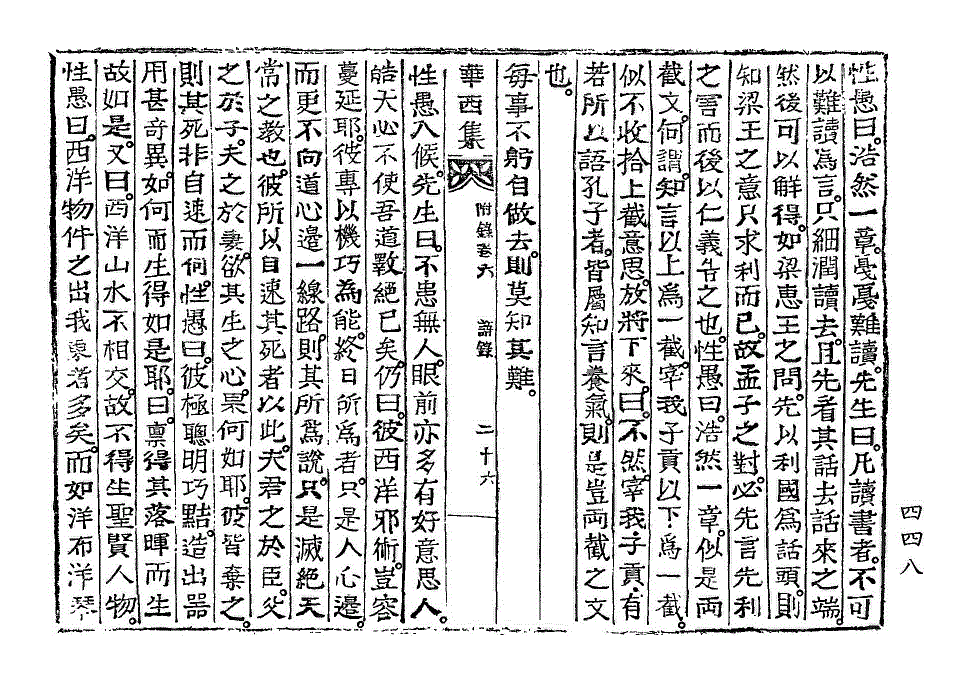 性愚曰。浩然一章。戛戛难读。先生曰。凡读书者。不可以难读为言。只细润读去。且先看其话去话来之端。然后可以解得。如梁惠王之问。先以利国为话头。则知梁王之意只求利而已。故孟子之对。必先言先利之害而后以仁义告之也。性愚曰。浩然一章。似是两截文。何谓。知言以上为一截。宰我子贡以下为一截。似不收拾上截意思。放将下来。曰。不然。宰我,子贡,有若所以语孔子者。皆属知言养气。则是岂两截之文也。
性愚曰。浩然一章。戛戛难读。先生曰。凡读书者。不可以难读为言。只细润读去。且先看其话去话来之端。然后可以解得。如梁惠王之问。先以利国为话头。则知梁王之意只求利而已。故孟子之对。必先言先利之害而后以仁义告之也。性愚曰。浩然一章。似是两截文。何谓。知言以上为一截。宰我子贡以下为一截。似不收拾上截意思。放将下来。曰。不然。宰我,子贡,有若所以语孔子者。皆属知言养气。则是岂两截之文也。每事不躬自做去。则莫知其难。
性愚入候。先生曰。不患无人。眼前亦多有好意思人。皓天必不使吾道斁绝已矣。仍曰。彼西洋邪术。岂容蔓延耶。彼专以机巧为能。终日所为者。只是人心边。而更不向道心边一线路。则其所为说。只是灭绝天常之教也。彼所以自速其死者以此。夫君之于臣。父之于子。夫之于妻。欲其生之心。果何如耶。彼皆弃之。则其死非自速而何。性愚曰。彼极聪明巧黠。造出器用甚奇异。如何而生得如是耶。曰。禀得其落晖而生故如是。又曰。西洋山水不相交。故不得生圣贤人物。性愚曰。西洋物件之出我东者多矣。而如洋布洋琴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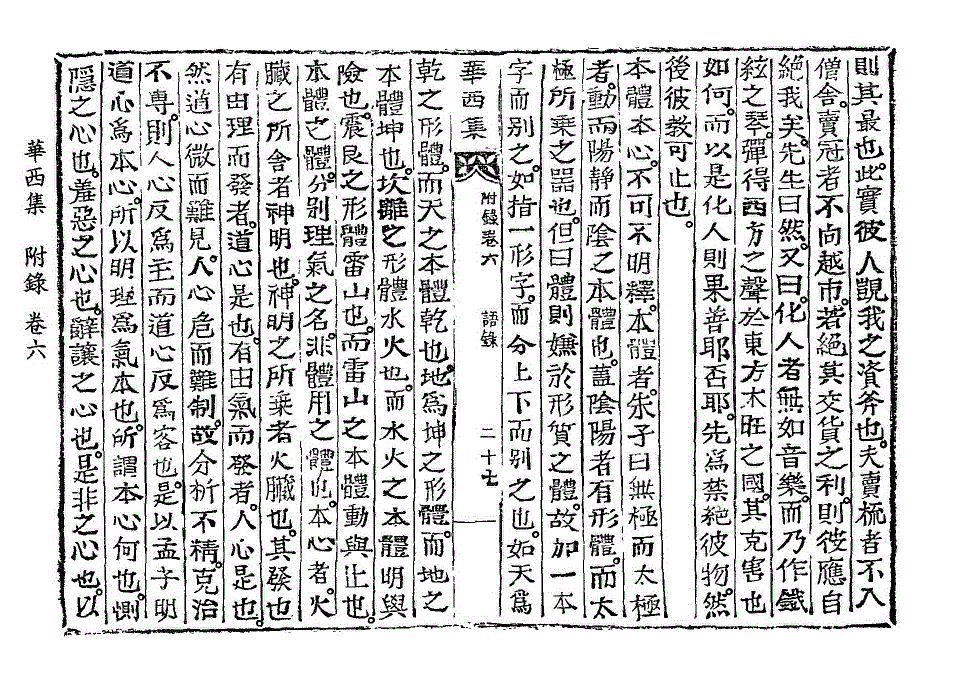 则其最也。此实彼人觊我之资斧也。夫卖梳者不入僧舍。卖冠者不向越市。若绝其交货之利。则彼应自绝我矣。先生曰然。又曰。化人者无如音乐。而乃作铁弦之琴。弹得西方之声于东方木旺之国。其克害也如何。而以是化人则果善耶否耶。先为禁绝彼物。然后彼教可止也。
则其最也。此实彼人觊我之资斧也。夫卖梳者不入僧舍。卖冠者不向越市。若绝其交货之利。则彼应自绝我矣。先生曰然。又曰。化人者无如音乐。而乃作铁弦之琴。弹得西方之声于东方木旺之国。其克害也如何。而以是化人则果善耶否耶。先为禁绝彼物。然后彼教可止也。本体本心。不可不明释。本体者。朱子曰无极而太极者。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盖阴阳者有形体。而太极所乘之器也。但曰体则嫌于形质之体。故加一本字而别之。如指一形字。而分上下而别之也。如天为乾之形体。而天之本体乾也。地为坤之形体。而地之本体坤也。坎离之形体水火也。而水火之本体明与险也。震艮之形体雷山也。而雷山之本体动与止也。本体之体。分别理气之名。非体用之体也。本心者。火脏之所舍者神明也。神明之所乘者火脏也。其发也有由理而发者。道心是也。有由气而发者。人心是也。然道心微而难见。人心危而难制。故分析不精。克治不专。则人心反为主而道心反为客也。是以孟子明道心为本心。所以明理为气本也。所谓本心何也。恻隐之心也。羞恶之心也。辞让之心也。是非之心也。以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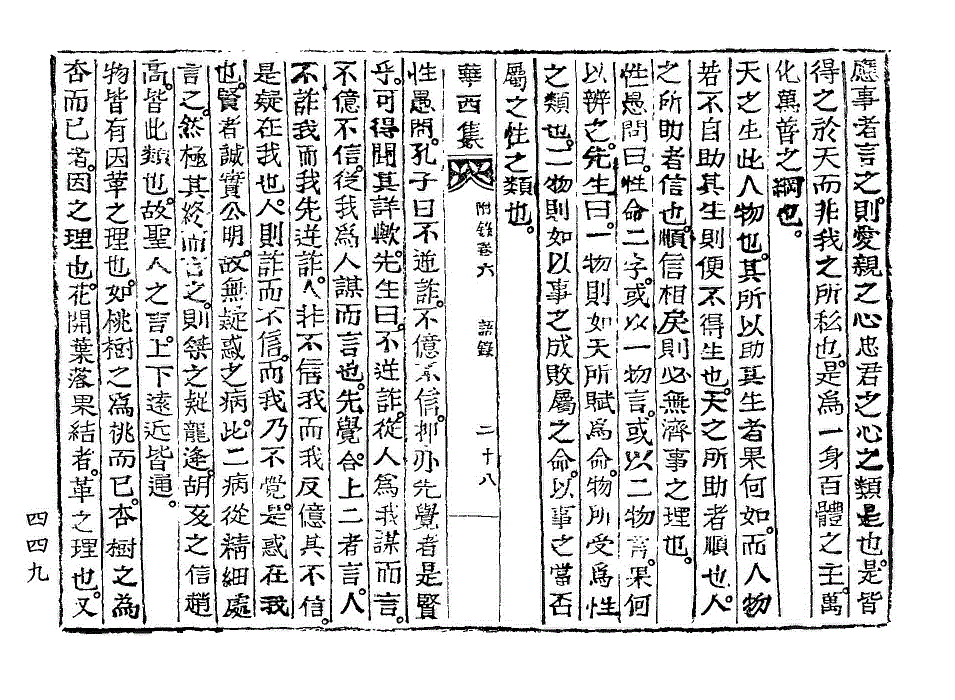 应事者言之。则爱亲之心忠君之心之类是也。是皆得之于天而非我之所私也。是为一身百体之主。万化万善之纲也。
应事者言之。则爱亲之心忠君之心之类是也。是皆得之于天而非我之所私也。是为一身百体之主。万化万善之纲也。天之生此人物也。其所以助其生者果何如。而人物若不自助其生则便不得生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顺信相戾则必无济事之理也。
性愚问曰。性命二字。或以一物言。或以二物言。果何以辨之。先生曰。一物则如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之类也。二物则如以事之成败属之命。以事之当否属之性之类也。
性愚问。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可得闻其详欤。先生曰。不逆诈。从人为我谋而言。不亿不信。从我为人谋而言也。先觉。合上二者言。人不诈我而我先逆诈。人非不信我而我反亿其不信。是疑在我也。人则诈而不信。而我乃不觉。是惑在我也。贤者诚实公明。故无疑惑之病。此二病从精细处言之。然极其终而言之。则桀之疑龙逄。胡亥之信赵高。皆此类也。故圣人之言。上下远近皆通。
物皆有因革之理也。如桃树之为桃而已。杏树之为杏而已者。因之理也。花开叶落果结者。革之理也。又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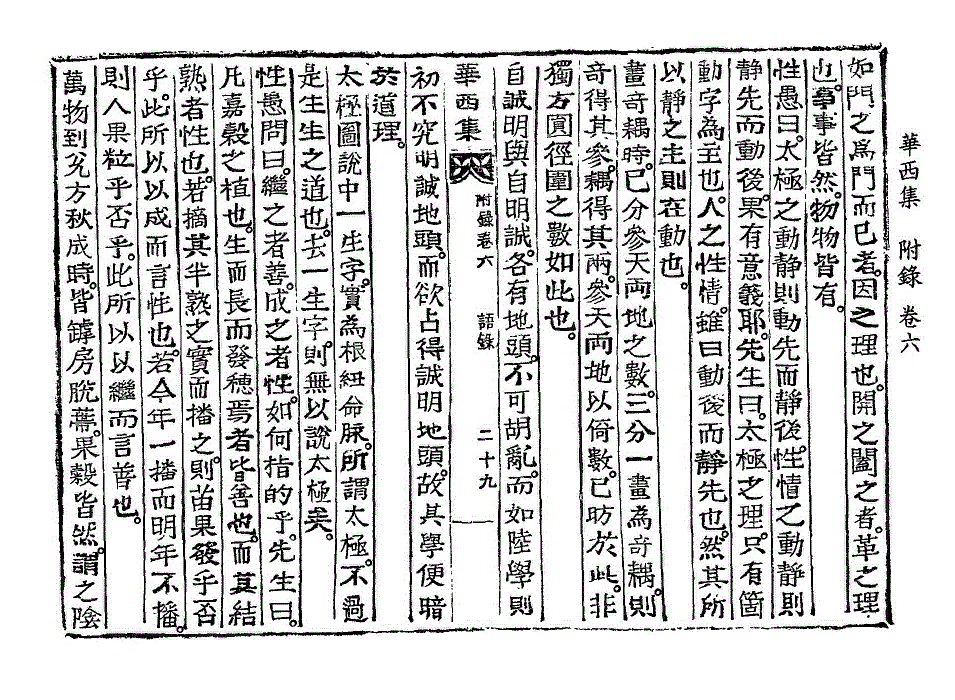 如门之为门而已者。因之理也。开之阖之者。革之理也。事事皆然。物物皆有。
如门之为门而已者。因之理也。开之阖之者。革之理也。事事皆然。物物皆有。性愚曰。太极之动静则动先而静后。性情之动静则静先而动后。果有意义耶。先生曰。太极之理。只有个动字为主也。人之性情。虽曰动后而静先也。然其所以静之主则在动也。
画奇耦时。已分参天两地之数。三分一画为奇耦。则奇得其参。耦得其两。参天两地以倚数。已昉于此。非独方圆径围之数如此也。
自诚明与自明诚。各有地头。不可胡乱。而如陆学则初不究明诚地头。而欲占得诚明地头。故其学便暗于道理。
太极图说中一生字。实为根纽命脉。所谓太极。不过是生生之道也。去一生字。则无以说太极矣。
性愚问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指的乎。先生曰。凡嘉谷之植也。生而长而发穗焉者皆善也。而其结熟者性也。若摘其半熟之实而播之。则苗果发乎否乎。此所以以成而言性也。若今年一播而明年不播。则人果粒乎否乎。此所以以继而言善也。
万物到兑方秋成时。皆罅房脱蒂。果谷皆然。谓之阴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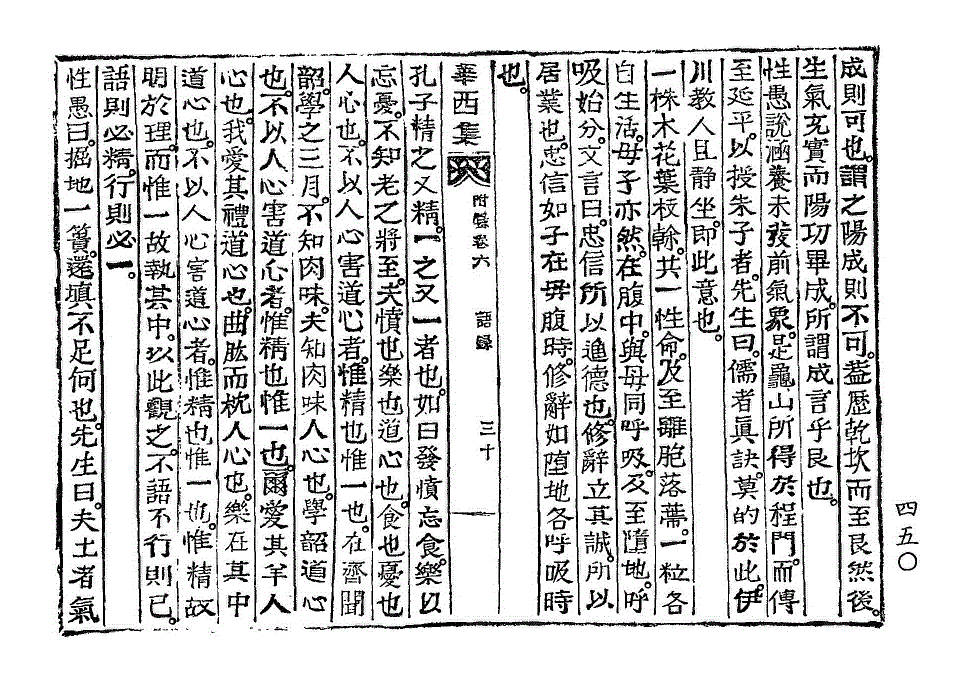 成则可也。谓之阳成则不可。盖历乾坎而至艮然后。生气充实而阳功毕成。所谓成言乎艮也。
成则可也。谓之阳成则不可。盖历乾坎而至艮然后。生气充实而阳功毕成。所谓成言乎艮也。性愚说涵养未发前气象。是龟山所得于程门。而传至延平。以授朱子者。先生曰。儒者真诀。莫的于此。伊川教人且静坐。即此意也。
一株木花叶枝干。共一性命。及至离胞落蒂。一粒各自生活。母子亦然。在腹中。与母同呼吸。及至堕地。呼吸始分。文言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忠信如子在母腹时。修辞如堕地各呼吸时也。
孔子精之又精。一之又一者也。如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夫愤也乐也道心也。食也忧也人心也。不以人心害道心者。惟精也惟一也。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夫知肉味人心也。学韶道心也。不以人心害道心者。惟精也惟一也。尔爱其羊人心也。我爱其礼道心也。曲肱而枕人心也。乐在其中道心也。不以人心害道心者。惟精也惟一也。惟精故明于理。而惟一故执其中。以此观之。不语不行则已。语则必精。行则必一。
性愚曰。掘地一篑。还填不足何也。先生曰。夫土者气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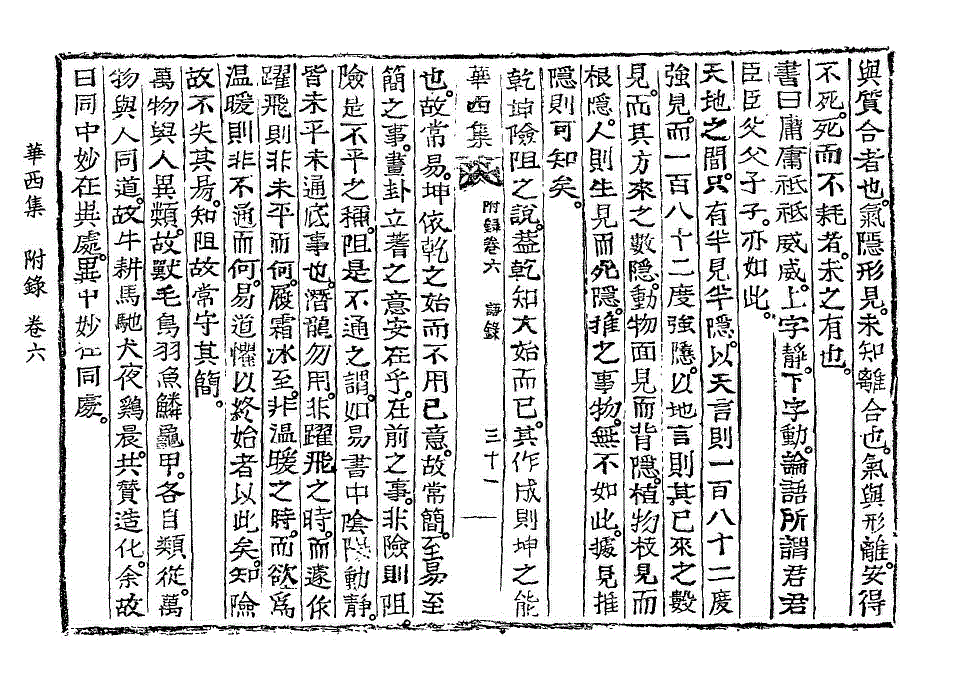 与质合者也。气隐形见。未知离合也。气与形离。安得不死。死而不耗者。未之有也。
与质合者也。气隐形见。未知离合也。气与形离。安得不死。死而不耗者。未之有也。书曰庸庸祗祗威威。上字静。下字动。论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亦如此。
天地之间。只有半见半隐。以天言则一百八十二度强见。而一百八十二度强隐。以地言则其已来之数见。而其方来之数隐。动物面见而背隐。植物枝见而根隐。人则生见而死隐。推之事物。无不如此。据见推隐则可知矣。
乾坤险阻之说。盖乾知大始而已。其作成则坤之能也。故常易。坤依乾之始而不用己意。故常简。至易至简之事。画卦立蓍之意安在乎。在前之事。非险则阻。险是不平之称。阻是不通之谓。如易书中阴阳动静。皆未平未通底事也。潜龙勿用。非跃飞之时。而遽作跃飞则非未平而何。履霜冰至。非温暖之时。而欲为温暖则非不通而何。易道惧以终始者以此矣。知险故不失其易。知阻故常守其简。
万物与人异类。故兽毛鸟羽鱼鳞龟甲。各自类从。万物与人同道。故牛耕马驰犬夜鸡晨。共赞造化。余故曰同中妙在异处。异中妙在同处。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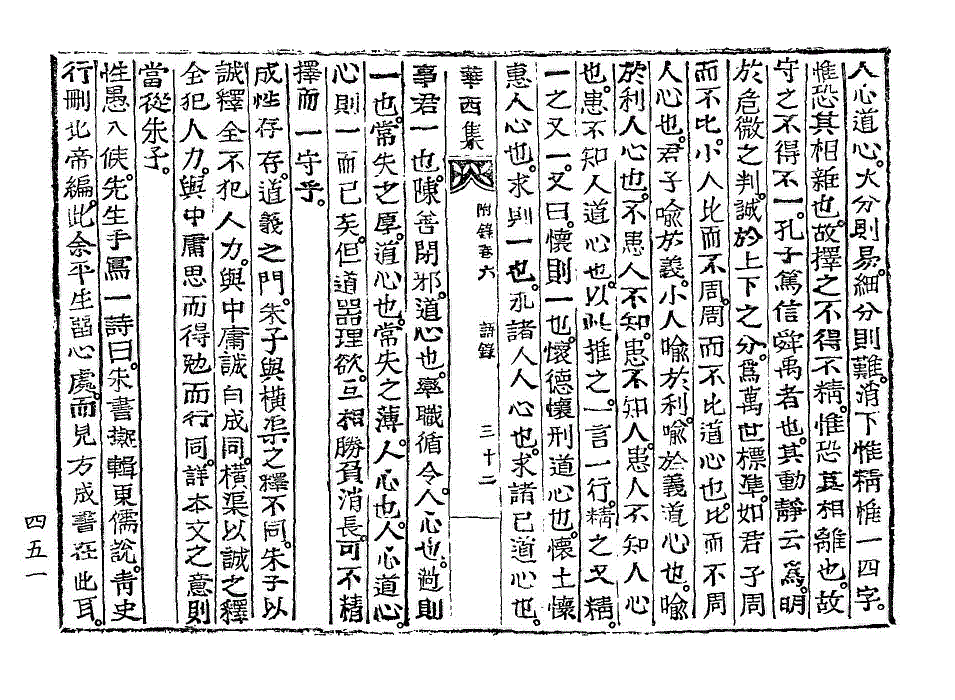 人心道心。大分则易。细分则难。消下惟精惟一四字。惟恐其相杂也。故择之不得不精。惟恐其相离也。故守之不得不一。孔子笃信舜禹者也。其动静云为。明于危微之判。诚于上下之分。为万世标准。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而不比道心也。比而不周人心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义道心也。喻于利人心也。不患人不知。患不知人。患人不知人心也。患不知人道心也。以此推之。一言一行。精之又精。一之又一。又曰。怀则一也。怀德怀刑道心也。怀土怀惠人心也。求则一也。求诸人人心也。求诸己道心也。事君一也。陈善闭邪。道心也。率职循令。人心也。过则一也。常失之厚。道心也。常失之薄。人心也。人心道心。心则一而已矣。但道器理欲。互相胜负消长。可不精择而一守乎。
人心道心。大分则易。细分则难。消下惟精惟一四字。惟恐其相杂也。故择之不得不精。惟恐其相离也。故守之不得不一。孔子笃信舜禹者也。其动静云为。明于危微之判。诚于上下之分。为万世标准。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而不比道心也。比而不周人心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于义道心也。喻于利人心也。不患人不知。患不知人。患人不知人心也。患不知人道心也。以此推之。一言一行。精之又精。一之又一。又曰。怀则一也。怀德怀刑道心也。怀土怀惠人心也。求则一也。求诸人人心也。求诸己道心也。事君一也。陈善闭邪。道心也。率职循令。人心也。过则一也。常失之厚。道心也。常失之薄。人心也。人心道心。心则一而已矣。但道器理欲。互相胜负消长。可不精择而一守乎。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朱子与横渠之释不同。朱子以诚释全不犯人力。与中庸诚自成同。横渠以诚之释全犯人力。与中庸思而得勉而行同。详本文之意则当从朱子。
性愚入候。先生手写一诗曰。朱书拟辑东儒说。青史行删北帝编。此余平生留心处。而见方成书在此耳。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2H 页
 华东史合编纲目编次之日。有欲删宋高宗正统之说。而余以为高宗宋帝之适嗣也。又况朱子之所君。则岂可轻删耶。以此止之矣。今又考之则朱子请高宗世室。而尤庵己巳遗疏。有曰昔朱子生乎高宗之世。出身以事。而高宗崩。建请为世室。夫高宗忘亲事雠之君也。犹以建事艰难不殄宗社为功云云。其义又可见矣。
华东史合编纲目编次之日。有欲删宋高宗正统之说。而余以为高宗宋帝之适嗣也。又况朱子之所君。则岂可轻删耶。以此止之矣。今又考之则朱子请高宗世室。而尤庵己巳遗疏。有曰昔朱子生乎高宗之世。出身以事。而高宗崩。建请为世室。夫高宗忘亲事雠之君也。犹以建事艰难不殄宗社为功云云。其义又可见矣。显诸仁藏诸用。一时说亦得。先后说亦得。盖横说则仁义礼智。一时皆备。竖说则元了而亨。亨了而利。利了而贞。贞复生元。此则横说竖说虽异。其不犯人力一也。朱子之释。盖亦如此。而但学之者。未分两边说。故随其所闻。只会录出一边耳。
朱子以亚圣之姿。尽致曲之学。
朱子注释孔子。一一从肚里过。故得孔子之心。莫如朱子。
严于省察。确于积累。为学之要也。于气中省察其无质者。(声色臭味之类。)于理中积累其有迹者。(心性情。)
己字有二义。孔子曰克己复礼。又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之己。在所当祛。由己之己。在所当勉。二者不可不审。一为私意惹绊。二为推诿别人。又云己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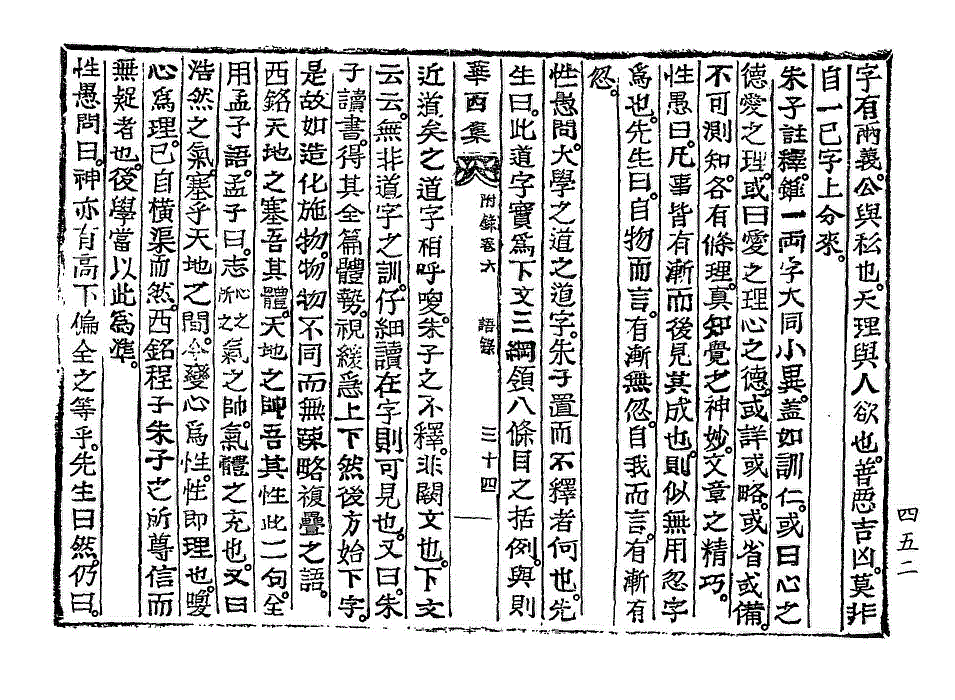 字有两义。公与私也。天理与人欲也。善恶吉凶。莫非自一己字上分来。
字有两义。公与私也。天理与人欲也。善恶吉凶。莫非自一己字上分来。朱子注释。虽一两字大同小异。盖如训仁。或曰心之德爱之理。或曰爱之理心之德。或详或略。或省或备。不可测知。各有条理。真知觉之神妙。文章之精巧。
性愚曰。凡事皆有渐而后见其成也。则似无用忽字为也。先生曰。自物而言。有渐无忽。自我而言。有渐有忽。
性愚问。大学之道之道字。朱子置而不释者何也。先生曰。此道字实为下文三纲领八条目之括例。与则近道矣之道字相呼唤。朱子之不释。非阙文也。下文云云。无非道字之训。仔细读在字则可见也。又曰。朱子读书。得其全篇体势。视缓急上下然后方始下字。是故如造化施物。物物不同而无疏略复叠之语。
西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二句。全用孟子语。孟子曰。志(心之所之)气之帅。气体之充也。又曰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今变心为性。性即理也。唤心为理。已自横渠而然。西铭程子朱子之所尊信而无疑者也。后学当以此为准。
性愚问曰。神亦有高下偏全之等乎。先生曰然。仍曰。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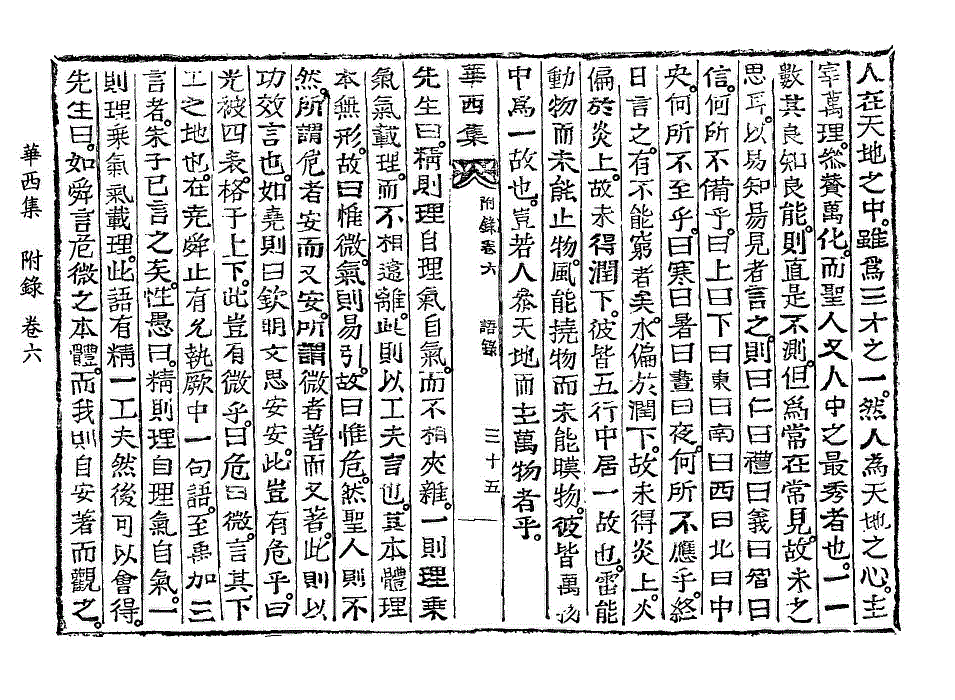 人在天地之中。虽为三才之一。然人为天地之心。主宰万理。参赞万化。而圣人又人中之最秀者也。一一数其良知良能。则直是不测。但为常在常见。故未之思耳。以易知易见者言之。则曰仁曰礼曰义曰智曰信。何所不备乎。曰上曰下曰东曰南曰西曰北曰中央。何所不至乎。曰寒曰暑曰昼曰夜。何所不应乎。终日言之。有不能穷者矣。水偏于润下。故未得炎上。火偏于炎上。故未得润下。彼皆五行中居一故也。雷能动物而未能止物。风能挠物而未能暵物。彼皆万物中为一故也。岂若人参天地而主万物者乎。
人在天地之中。虽为三才之一。然人为天地之心。主宰万理。参赞万化。而圣人又人中之最秀者也。一一数其良知良能。则直是不测。但为常在常见。故未之思耳。以易知易见者言之。则曰仁曰礼曰义曰智曰信。何所不备乎。曰上曰下曰东曰南曰西曰北曰中央。何所不至乎。曰寒曰暑曰昼曰夜。何所不应乎。终日言之。有不能穷者矣。水偏于润下。故未得炎上。火偏于炎上。故未得润下。彼皆五行中居一故也。雷能动物而未能止物。风能挠物而未能暵物。彼皆万物中为一故也。岂若人参天地而主万物者乎。先生曰。精则理自理气自气。而不相夹杂。一则理乘气气载理。而不相违离。此则以工夫言也。其本体理本无形。故曰惟微。气则易引。故曰惟危。然圣人则不然。所谓危者安而又安。所谓微者著而又著。此则以功效言也。如尧则曰钦明文思安安。此岂有危乎。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岂有微乎。曰危曰微。言其下工之地也。在尧舜止有允执厥中一句语。至禹加三言者。朱子已言之矣。性愚曰。精则理自理气自气。一则理乘气气载理。此语有精一工夫然后可以会得。先生曰。如舜言危微之本体。而我则自安著而观之。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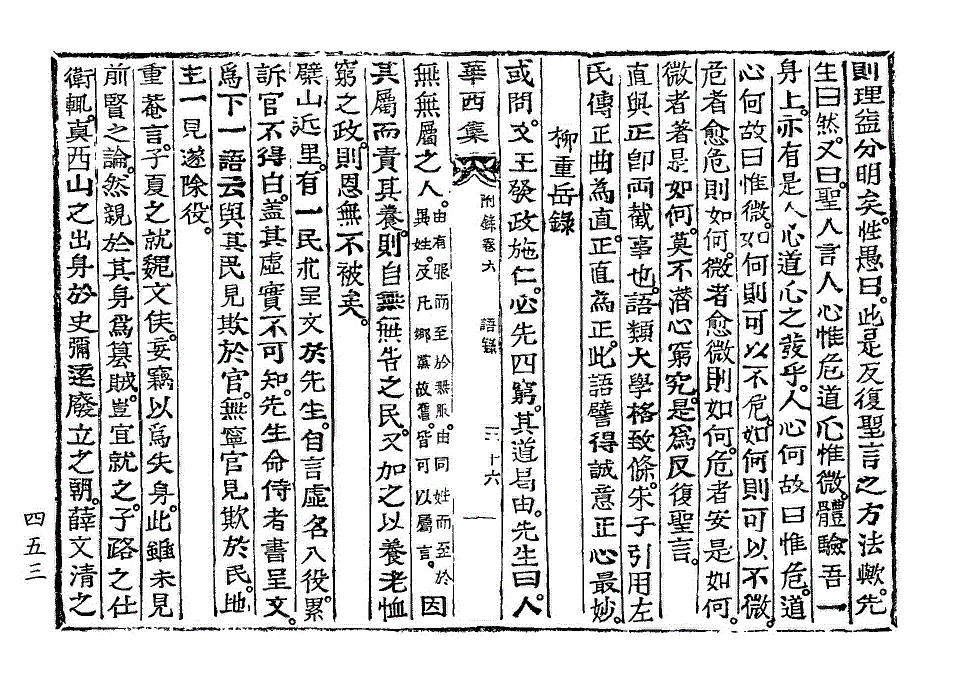 则理益分明矣。性愚曰。此是反复圣言之方法欤。先生曰然。又曰。圣人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体验吾一身上。亦有是人心道心之发乎。人心何故曰惟危。道心何故曰惟微。如何则可以不危。如何则可以不微。危者愈危则如何。微者愈微则如何。危者安是如何。微者著是如何。莫不潜心穷究。是为反复圣言。
则理益分明矣。性愚曰。此是反复圣言之方法欤。先生曰然。又曰。圣人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体验吾一身上。亦有是人心道心之发乎。人心何故曰惟危。道心何故曰惟微。如何则可以不危。如何则可以不微。危者愈危则如何。微者愈微则如何。危者安是如何。微者著是如何。莫不潜心穷究。是为反复圣言。直与正即两截事也。语类大学格致条。朱子引用左氏传正曲为直。正直为正。此语譬得诚意正心最妙。
柳重岳录
或问。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四穷。其道曷由。先生曰。人无无属之人。(由有服而至于无服。由同姓而至于异姓。及凡乡党故旧。皆可以属言。)因其属而责其养。则自无无告之民。又加之以养老恤穷之政。则恩无不被矣。
檗山近里。有一民求呈文于先生。自言虚名入役。累诉官不得白。盖其虚实不可知。先生命侍者书呈文。为下一语云与其民见欺于官。无宁官见欺于民。地主一见遂除役。
重庵言。子夏之就魏文侯。妄窃以为失身。此虽未见前贤之论。然亲于其身为篡贼。岂宜就之。子路之仕卫辄。真西山之出身于史弥远废立之朝。薛文清之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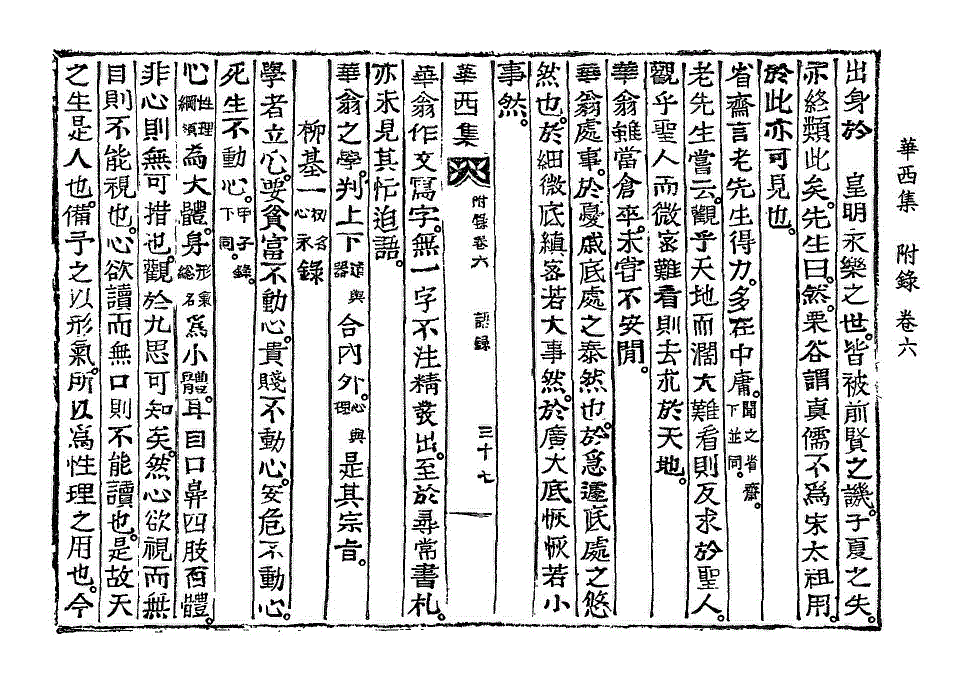 出身于 皇明永乐之世。皆被前贤之讥。子夏之失。亦终类此矣。先生曰。然。栗谷谓真儒不为宋太祖用。于此亦可见也。
出身于 皇明永乐之世。皆被前贤之讥。子夏之失。亦终类此矣。先生曰。然。栗谷谓真儒不为宋太祖用。于此亦可见也。省斋言老先生得力。多在中庸。(闻之省斋。下并同。)
老先生尝云。观乎天地而阔大难看则反求于圣人。观乎圣人而微密难看则去求于天地。
华翁虽当仓卒。未尝不安閒。
华翁处事。于忧戚底处之泰然也。于急遽底处之悠然也。于细微底缜密若大事然。于广大底恢恢若小事然。
华翁作文写字。无一字不注精发出。至于寻常书札。亦未见其忙迫语。
华翁之学。判上下(道与器)合内外。(心与理)是其宗旨。
柳基一(初名心永)录
学者立心。要贫富不动心。贵贱不动心。安危不动心。死生不动心。(甲子录。下同。)
心(性理纲领)为大体。身(形气总名)为小体。耳目口鼻四肢百体。非心则无可措也。观于九思可知矣。然心欲视而无目则不能视也。心欲读而无口则不能读也。是故天之生是人也。备予之以形气。所以为性理之用也。今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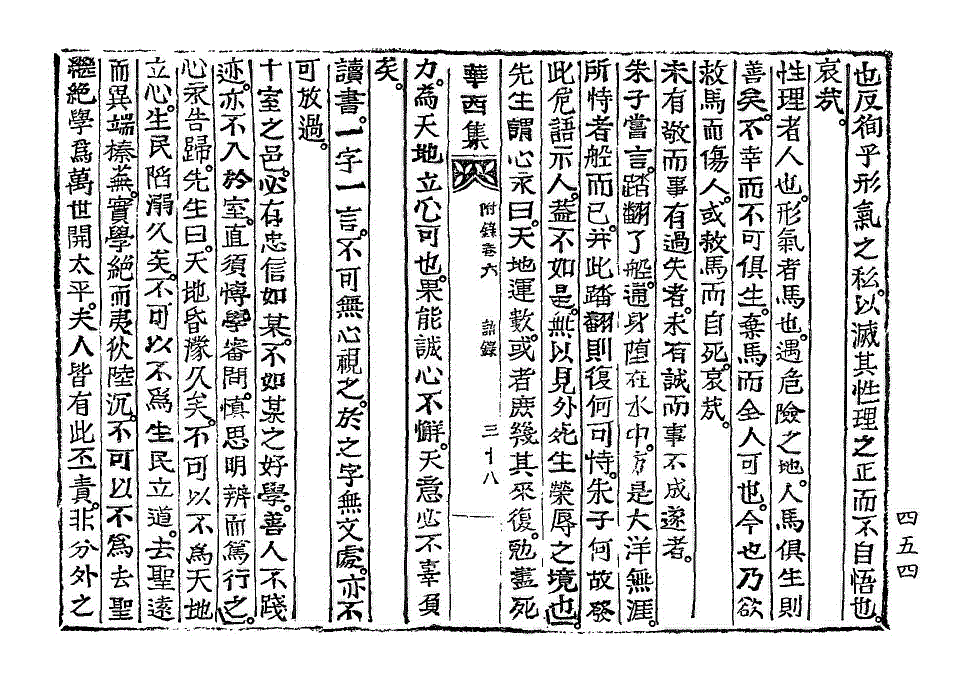 也反徇乎形气之私。以灭其性理之正而不自悟也。哀哉。
也反徇乎形气之私。以灭其性理之正而不自悟也。哀哉。性理者人也。形气者马也。遇危险之地。人马俱生则善矣。不幸而不可俱生。弃马而全人可也。今也乃欲救马而伤人。或救马而自死。哀哉。
未有敬而事有过失者。未有诚而事不成遂者。
朱子尝言。踏翻了船。通身堕在水中。方是大洋无涯。所恃者船而已。并此踏翻则复何可恃。朱子何故发此危语示人。盖不如是。无以见外死生荣辱之境也。
先生谓心永曰。天地运数。或者庶几其来复。勉尽死力。为天地立心可也。果能诚心不懈。天意必不辜负矣。
读书。一字一言。不可无心视之。于之字无文处。亦不可放过。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不如某之好学。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直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
心永告归。先生曰。天地昏濛久矣。不可以不为天地立心。生民陷溺久矣。不可以不为生民立道。去圣远而异端榛芜。实学绝而夷狄陆沉。不可以不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夫人皆有此丕责。非分外之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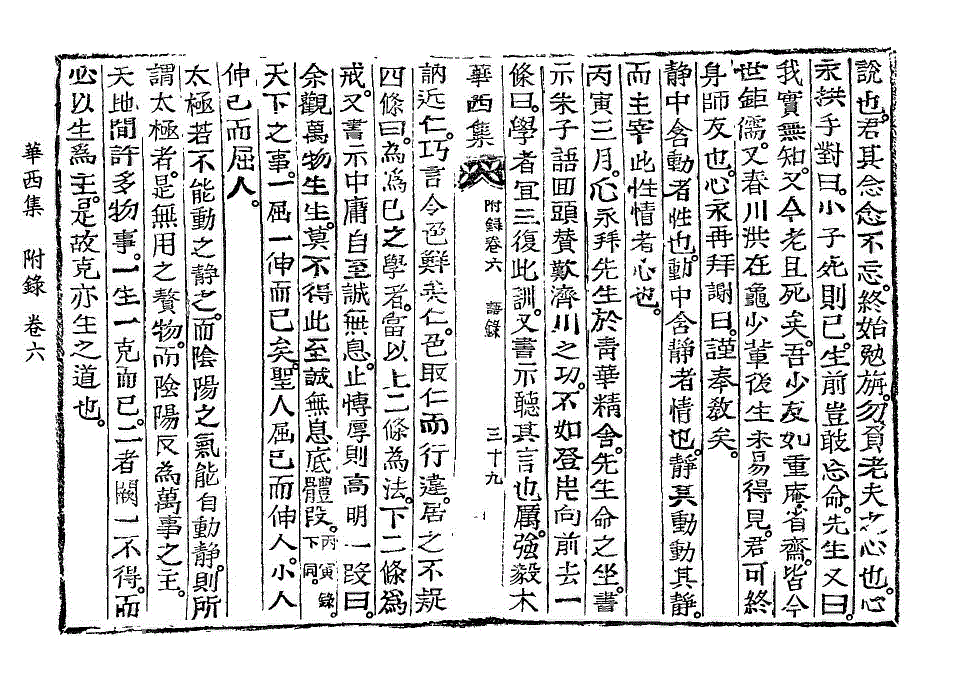 说也。君其念念不忘。终始勉旃。勿负老夫之心也。心永拱手对曰。小子死则已。生前岂敢忘命。先生又曰。我实无知。又今老且死矣。吾少友如重庵,省斋。皆今世钜儒。又春川洪在龟少辈后生未易得见。君可终身师友也。心永再拜谢曰。谨奉教矣。
说也。君其念念不忘。终始勉旃。勿负老夫之心也。心永拱手对曰。小子死则已。生前岂敢忘命。先生又曰。我实无知。又今老且死矣。吾少友如重庵,省斋。皆今世钜儒。又春川洪在龟少辈后生未易得见。君可终身师友也。心永再拜谢曰。谨奉教矣。静中含动者性也。动中含静者情也。静其动动其静。而主宰此性情者心也。
丙寅三月。心永拜先生于青华精舍。先生命之坐。书示朱子语回头赞叹济川之功。不如登岸向前去一条曰。学者宜三复此训。又书示听其言也厉。强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四条曰。为为己之学者。当以上二条为法。下二条为戒。又书示中庸自至诚无息。止博厚则高明一段曰。余观万物生生。莫不得此至诚无息底体段。(丙寅录。下同。)
天下之事。一屈一伸而已矣。圣人屈己而伸人。小人伸己而屈人。
太极若不能动之静之。而阴阳之气能自动静。则所谓太极者。是无用之赘物。而阴阳反为万事之主。
天地间许多物事。一生一克而已。二者阙一不得。而必以生为主。是故克亦生之道也。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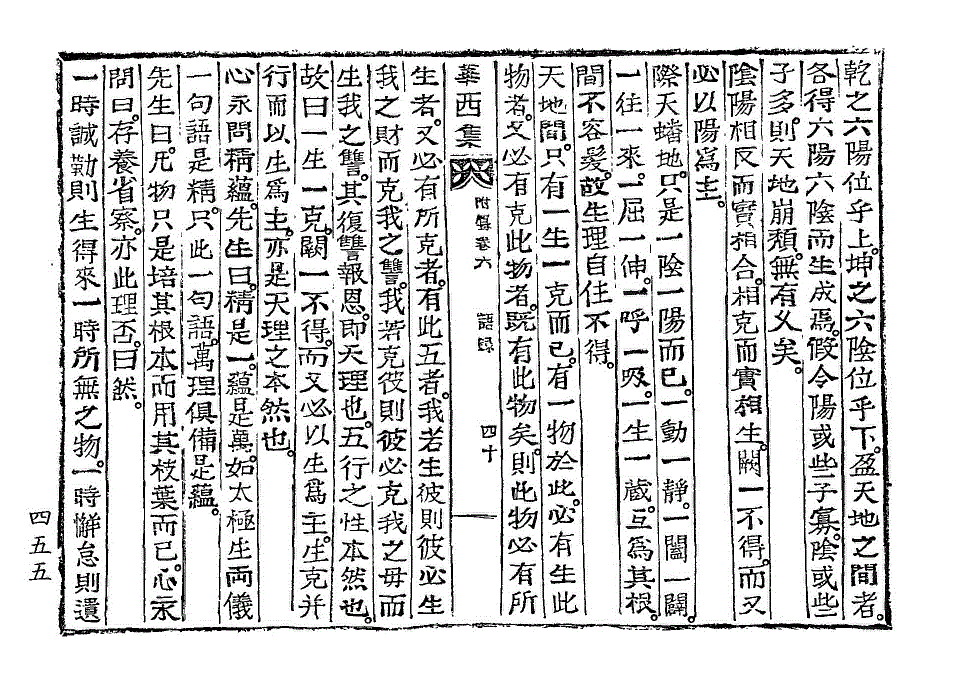 乾之六阳位乎上。坤之六阴位乎下。盈天地之间者。各得六阳六阴而生成焉。假令阳或些子寡。阴或些子多。则天地崩颓。无有久矣。
乾之六阳位乎上。坤之六阴位乎下。盈天地之间者。各得六阳六阴而生成焉。假令阳或些子寡。阴或些子多。则天地崩颓。无有久矣。阴阳相反而实相合。相克而实相生。阙一不得。而又必以阳为主。
际天蟠地。只是一阴一阳而已。一动一静。一阖一辟。一往一来。一屈一伸。一呼一吸。一生一藏。互为其根。间不容发。故生理自住不得。
天地间。只有一生一克而已。有一物于此。必有生此物者。又必有克此物者。既有此物矣。则此物必有所生者。又必有所克者。有此五者。我若生彼则彼必生我之财而克我之雠。我若克彼则彼必克我之母而生我之雠。其复雠报恩。即天理也。五行之性本然也。故曰一生一克。阙一不得。而又必以生为主。生克并行而以生为主。亦是天理之本然也。
心永问精蕴。先生曰。精是一。蕴是万。如太极生两仪一句语是精。只此一句语。万理俱备是蕴。
先生曰。凡物只是培其根本而用其枝叶而已。心永问曰。存养省察。亦此理否。曰然。
一时诚勤则生得来一时所无之物。一时懈怠则遗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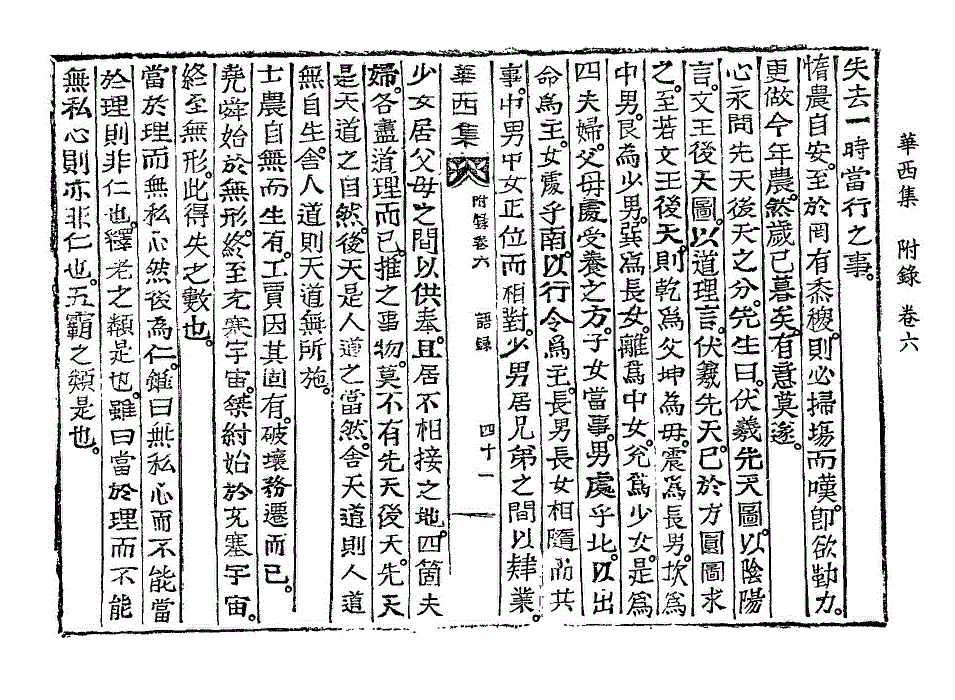 失去一时当行之事。
失去一时当行之事。惰农自安。至于罔有黍稷。则必扫场而叹。即欲勤力。更做今年农。然岁已暮矣。有意莫遂。
心永问先天后天之分。先生曰。伏羲先天图。以阴阳言。文王后天图。以道理言。伏羲先天。已于方圆图求之。至若文王后天。则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是为四夫妇。父母处受养之方。子女当事。男处乎北。以出命为王。女处乎南。以行令为主。长男长女相随而共事。中男中女正位而相对。少男居兄弟之间以肄业。少女居父母之间以供奉。且居不相接之地。四个夫妇。各尽道理而已。推之事物。莫不有先天后天。先天是天道之自然。后天是人道之当然。舍天道则人道无自生。舍人道则天道无所施。
士农自无而生有。工贾因其固有。破坏务迁而已。
尧舜始于无形。终至充塞宇宙。桀纣始于充塞宇宙。终至无形。此得失之数也。
当于理而无私心然后为仁。虽曰无私心而不能当于理则非仁也。释老之类是也。虽曰当于理而不能无私心则亦非仁也。五霸之类是也。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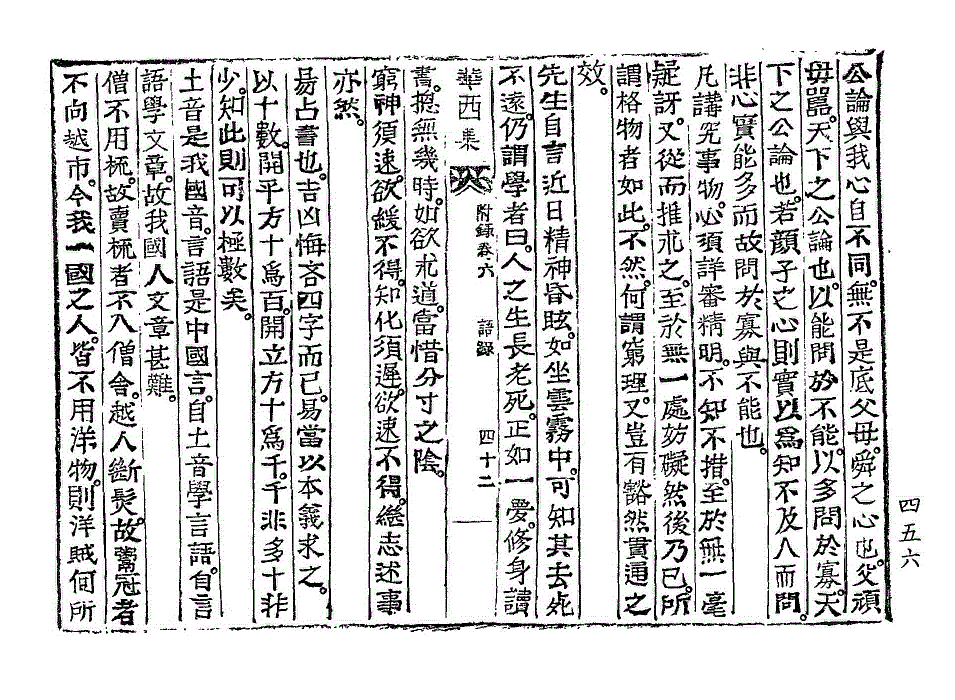 公论与我心自不同。无不是底父母。舜之心也。父顽母嚚。天下之公论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天下之公论也。若颜子之心则实以为知不及人而问。非心实能多而故问于寡与不能也。
公论与我心自不同。无不是底父母。舜之心也。父顽母嚚。天下之公论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天下之公论也。若颜子之心则实以为知不及人而问。非心实能多而故问于寡与不能也。凡讲究事物。必须详审精明。不知不措。至于无一毫疑讶。又从而推求之。至于无一处妨碍然后乃已。所谓格物者如此。不然。何谓穷理。又岂有豁然贯通之效。
先生自言近日精神昏眩。如坐云雾中。可知其去死不远。仍谓学者曰。人之生长老死。正如一梦。修身读书。总无几时。如欲求道。当惜分寸之阴。
穷神须速。欲缓不得。知化须迟。欲速不得。继志述事亦然。
易占书也。吉凶悔吝四字而已。易当以本义求之。
以十数。开平方十为百。开立方十为千。千非多十非少。知此则可以极数矣。
土音是我国音。言语是中国言。自土音学言语。自言语学文章。故我国人文章甚难。
僧不用梳。故卖梳者不入僧舍。越人断发。故鬻冠者不向越市。今我一国之人。皆不用洋物。则洋贼何所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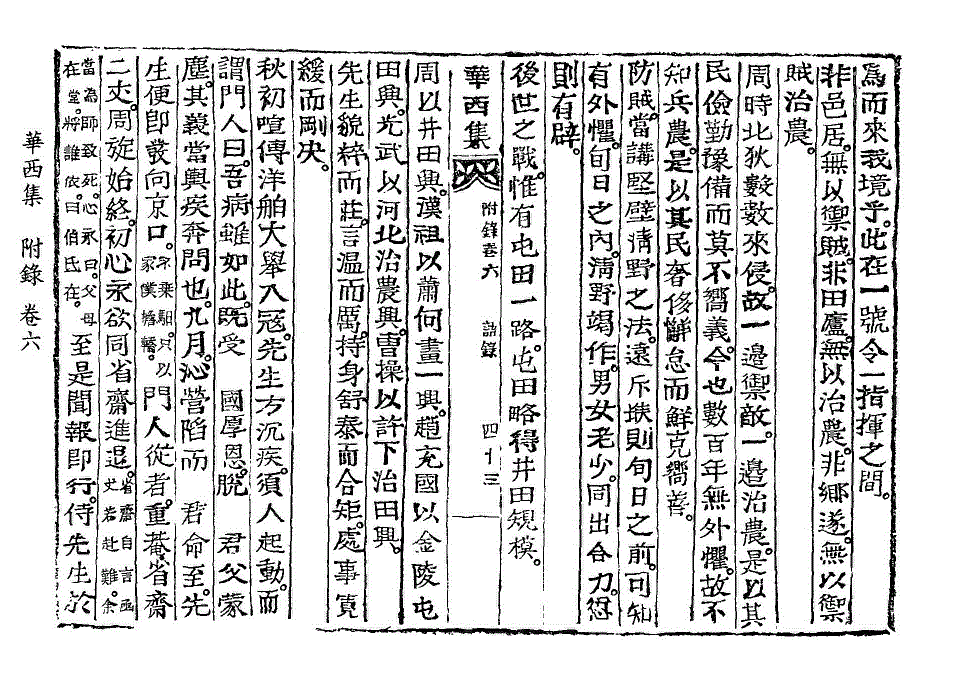 为而来我境乎。此在一号令一指挥之间。
为而来我境乎。此在一号令一指挥之间。非邑居。无以御贼。非田庐。无以治农。非乡遂。无以御贼治农。
周时北狄数数来侵。故一边御敌。一边治农。是以其民俭勤豫备而莫不向义。今也数百年无外惧。故不知兵农。是以其民奢侈懈怠而鲜克向善。
防贼。当讲坚壁清野之法。远斥堠则旬日之前。可知有外惧。旬日之内。清野竭作。男女老少。同出合力。愆则有辟。
后世之战。惟有屯田一路。屯田略得井田规模。
周以井田兴。汉祖以萧何画一兴。赵充国以金陵屯田兴。光武以河北治农兴。曹操以许下治田兴。
先生貌粹而庄。言温而厉。持身舒泰而合矩。处事宽缓而刚决。
秋初喧传洋舶大举入寇。先生方沉疾。须人起动。而谓门人曰。吾病虽如此。既受 国厚恩。脱 君父蒙尘。其义当舆疾奔问也。九月。沁营陷而 君命至。先生便即发向京口。(不乘驲。只以家仆担轿。)门人从者。重庵,省斋二丈。周旋始终。初心永欲同省斋进退。(省斋自言函丈若赴难。余当为师致死。心永曰。父母在堂。将谁依。曰伯氏在。)至是闻报即行。侍先生于
华西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六 第 4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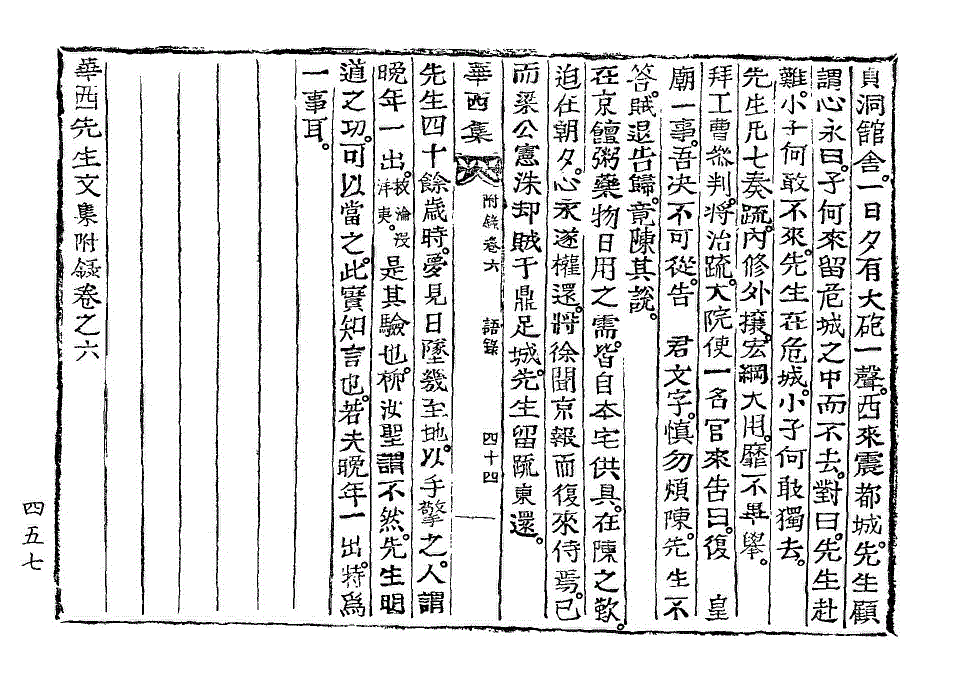 贞洞馆舍。一日夕有大炮一声。西来震都城。先生顾谓心永曰。子何来留危城之中而不去。对曰。先生赴难。小子何敢不来。先生在危城。小子何敢独去。
贞洞馆舍。一日夕有大炮一声。西来震都城。先生顾谓心永曰。子何来留危城之中而不去。对曰。先生赴难。小子何敢不来。先生在危城。小子何敢独去。先生凡七奏疏。内修外攘。宏纲大用。靡不毕举。
拜工曹参判。将治疏。大院使一名官来告曰。复 皇庙一事。吾决不可从。告 君文字。慎勿烦陈。先生不答。贼退告归。竟陈其说。
在京饘粥药物日用之需。皆自本宅供具。在陈之叹。迫在朝夕。心永遂权还。将徐闻京报而复来侍焉。已而梁公宪洙却贼于鼎足城。先生留疏东还。
先生四十馀岁时。梦见日坠几至地。以手擎之。人谓晚年一出。(救沦没洋夷。)是其验也。柳汝圣谓不然。先生明道之功。可以当之。此实知言也。若夫晚年一出。特为一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