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x 页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杂著
杂著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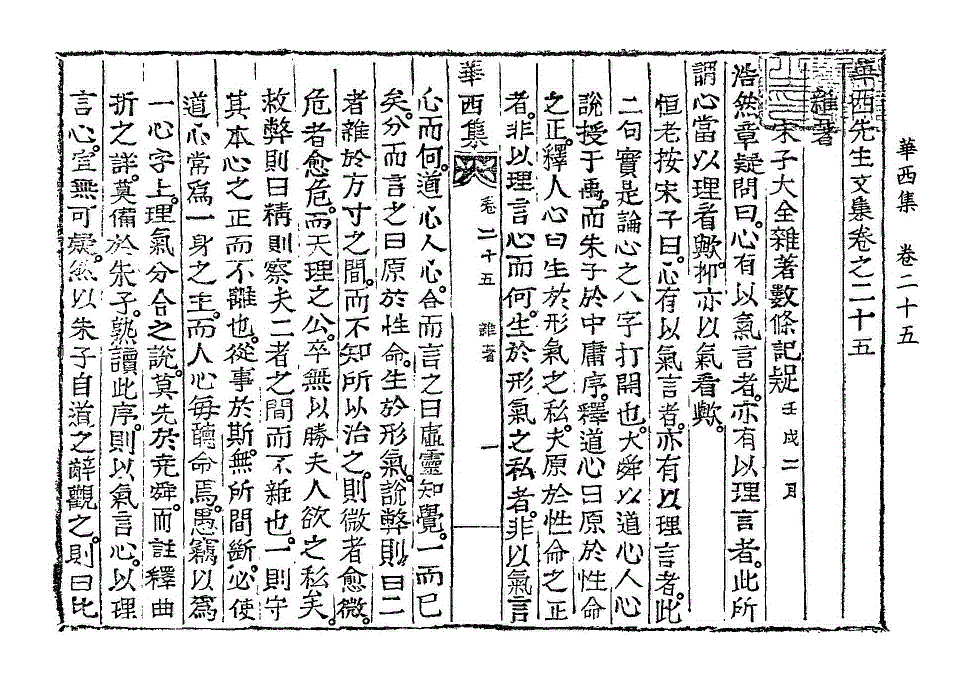 宋子大全杂著数条记疑(壬戌二月)
宋子大全杂著数条记疑(壬戌二月)浩然章疑问曰。心有以气言者。亦有以理言者。此所谓心当以理看欤。抑亦以气看欤。
恒老按宋子曰。心有以气言者。亦有以理言者。此二句实是论心之八字打开也。大舜以道心人心说授于禹。而朱子于中庸序。释道心曰原于性命之正。释人心曰生于形气之私。夫原于性命之正者。非以理言心而何。生于形气之私者。非以气言心而何。道心人心。合而言之曰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分而言之曰原于性命。生于形气。说弊则曰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微者愈微。危者愈危。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救弊则曰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所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愚窃以为一心字上。理气分合之说。莫先于尧舜。而注释曲折之详。莫备于朱子。熟读此序。则以气言心。以理言心。宜无可疑。然以朱子自道之辞观之。则曰比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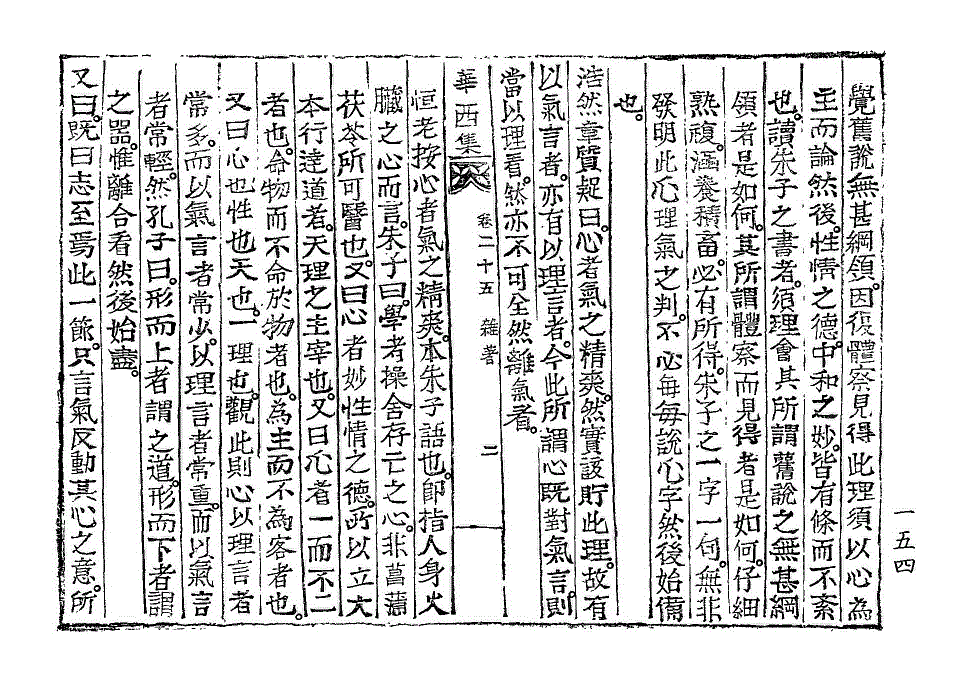 觉旧说无甚纲领。因复体察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然后。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也。读朱子之书者。须理会其所谓旧说之无甚纲领者是如何。其所谓体察而见得者是如何。仔细熟复。涵养积畜。必有所得。朱子之一字一句。无非发明此心理气之判。不必每每说心字然后始备也。
觉旧说无甚纲领。因复体察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然后。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也。读朱子之书者。须理会其所谓旧说之无甚纲领者是如何。其所谓体察而见得者是如何。仔细熟复。涵养积畜。必有所得。朱子之一字一句。无非发明此心理气之判。不必每每说心字然后始备也。浩然章质疑曰。心者气之精爽。然实该贮此理。故有以气言者。亦有以理言者。今此所谓心既对气言。则当以理看。然亦不可全然离气看。
恒老按心者气之精爽。本朱子语也。即指人身火脏之心而言。朱子曰。学者操舍存亡之心。非菖蒲茯苓所可医也。又曰心者妙性情之德。所以立大本行达道者。天理之主宰也。又曰心者一而不二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又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观此则心以理言者常多。而以气言者常少。以理言者常重。而以气言者常轻。然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惟离合看然后始尽。
又曰。既曰志至焉此一节。只言气反动其心之意。所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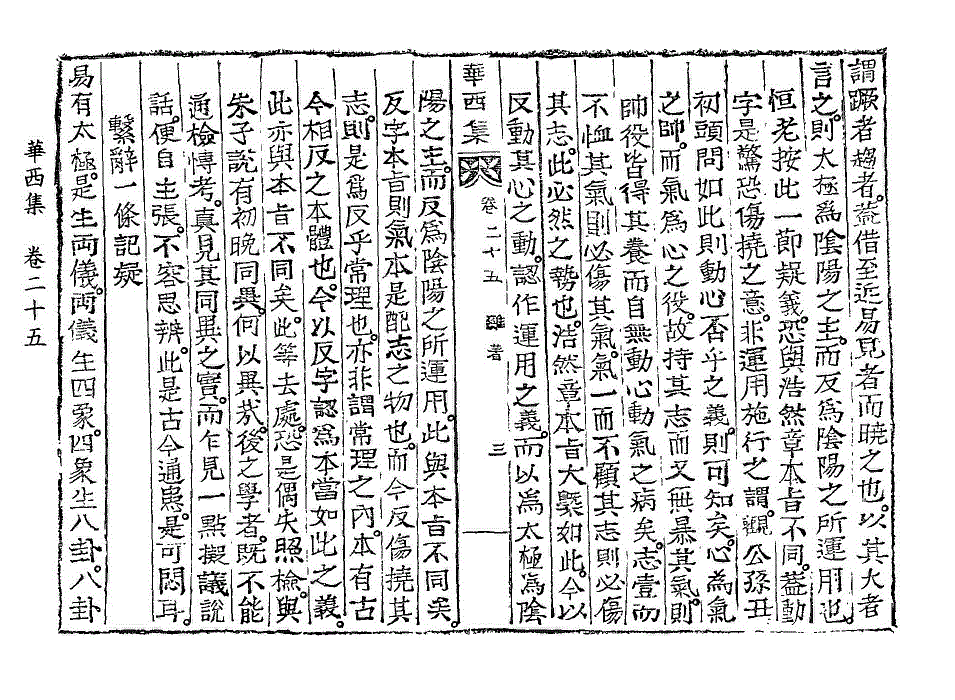 谓蹶者趋者。盖借至近易见者而晓之也。以其大者言之。则太极为阴阳之主。而反为阴阳之所运用也。
谓蹶者趋者。盖借至近易见者而晓之也。以其大者言之。则太极为阴阳之主。而反为阴阳之所运用也。恒老按此一节疑义。恐与浩然章本旨不同。盖动字是惊恐伤挠之意。非运用施行之谓。观公孙丑初头问如此则动心否乎之义。则可知矣。心为气之帅。而气为心之役。故持其志而又无暴其气。则帅役皆得其养而自无动心动气之病矣。志壹而不恤其气则必伤其气。气一而不顾其志则必伤其志。此必然之势也。浩然章本旨大槩如此。今以反动其心之动。认作运用之义。而以为太极为阴阳之主。而反为阴阳之所运用。此与本旨不同矣。反字本旨则气本是配志之物也。而今反伤挠其志。则是为反乎常理也。亦非谓常理之内。本有古今相反之本体也。今以反字认为本当如此之义。此亦与本旨不同矣。此等去处。恐是偶失照检。与朱子说有初晚同异。何以异哉。后之学者。既不能通检博考。真见其同异之实。而乍见一点拟议说话。便自主张。不容思辨。此是古今通患。是可闷耳。
系辞一条记疑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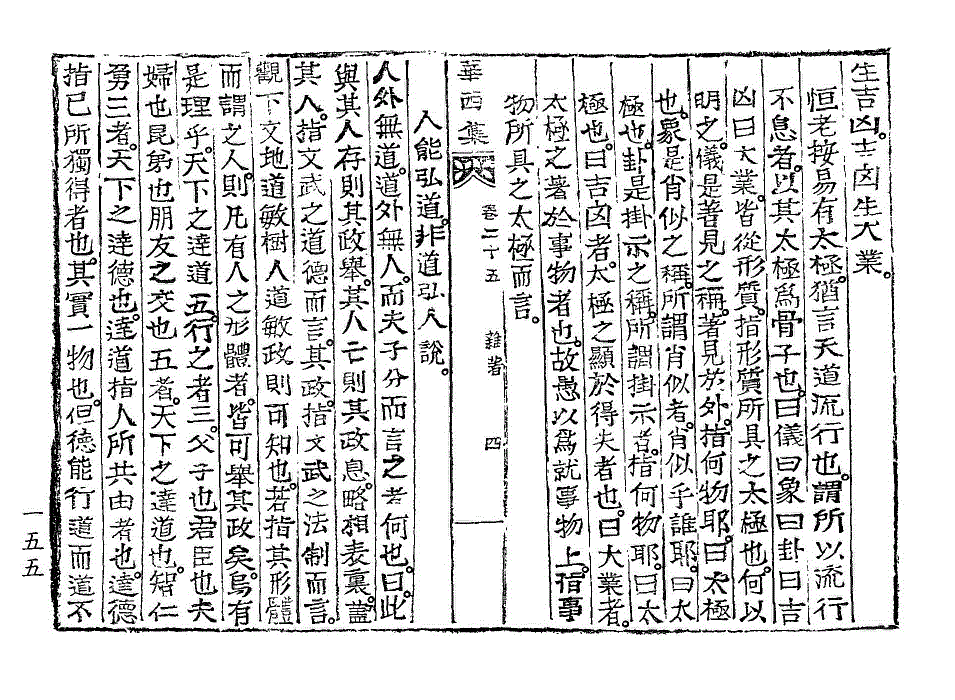 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恒老按易有太极。犹言天道流行也。谓所以流行不息者。以其太极为骨子也。曰仪曰象曰卦曰吉凶曰大业。皆从形质。指形质所具之太极也。何以明之。仪是著见之称。著见于外。指何物耶。曰太极也。象是肖似之称。所谓肖似者。肖似乎谁耶。曰太极也。卦是挂示之称。所谓挂示者。指何物耶。曰太极也。曰吉凶者。太极之显于得失者也。曰大业者。太极之著于事物者也。故愚以为就事物上。指事物所具之太极而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
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而夫子分而言之者何也。曰。此与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略相表里。盖其人。指文武之道德而言。其政。指文武之法制而言。观下文地道敏树人道敏政则可知也。若指其形体而谓之人。则凡有人之形体者。皆可举其政矣。乌有是理乎。天下之达道五。行之者三。父子也君臣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达道指人所共由者也。达德指己所独得者也。其实一物也。但德能行道而道不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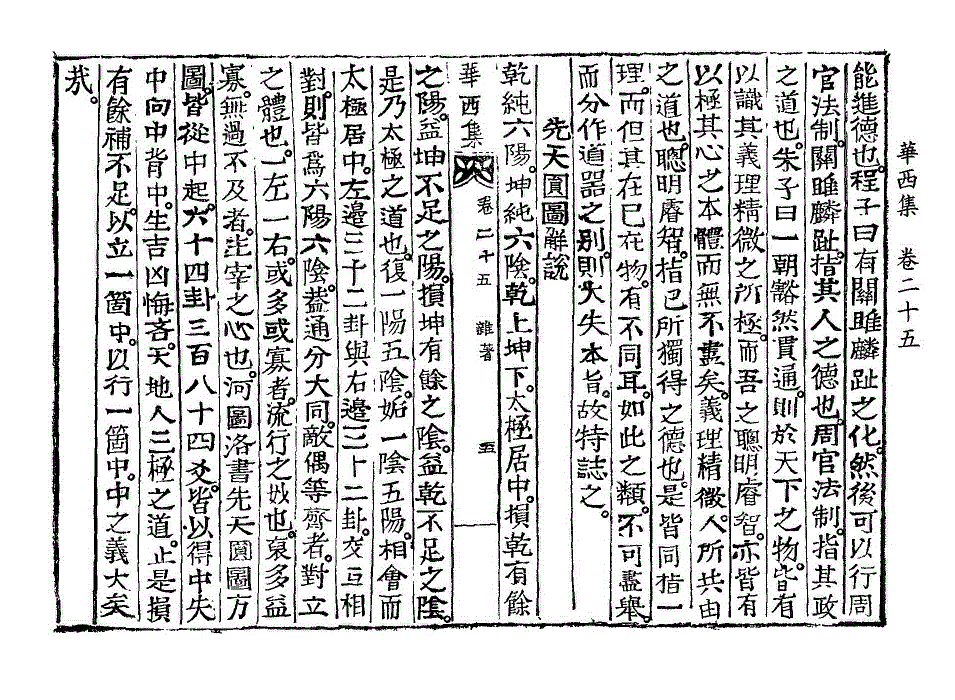 能进德也。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化。然后可以行周官法制。关雎麟趾。指其人之德也。周官法制。指其政之道也。朱子曰一朝豁然贯通。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识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义理精微。人所共由之道也。聪明睿智。指己所独得之德也。是皆同指一理。而但其在己在物。有不同耳。如此之类。不可尽举。而分作道器之别。则大失本旨。故特志之。
能进德也。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化。然后可以行周官法制。关雎麟趾。指其人之德也。周官法制。指其政之道也。朱子曰一朝豁然贯通。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识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义理精微。人所共由之道也。聪明睿智。指己所独得之德也。是皆同指一理。而但其在己在物。有不同耳。如此之类。不可尽举。而分作道器之别。则大失本旨。故特志之。先天圆图解说
乾纯六阳。坤纯六阴。乾上坤下。太极居中。损乾有馀之阳。益坤不足之阳。损坤有馀之阴。益乾不足之阴。是乃太极之道也。复一阳五阴。姤一阴五阳。相会而太极居中。左边三十二卦与右边三十二卦。交互相对。则皆为六阳六阴。盖通分大同。敌偶等齐者。对立之体也。一左一右。或多或寡者。流行之妙也。裒多益寡。无过不及者。主宰之心也。河图洛书先天圆图方图。皆从中起。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以得中失中向中背中。生吉凶悔吝。天地人三极之道。止是损有馀补不足。以立一个中。以行一个中。中之义大矣哉。
道器说
道者。四通五达之名。器者。适用一定之物。非道无以生养是器。非器无以承载是道。道是天地万物之至尊。器是天地万物之至宝。圣人下学而践其器。上达而明其道。故与天地合其德矣。众人不能下学。故器为空器。不能上达。故道非真道。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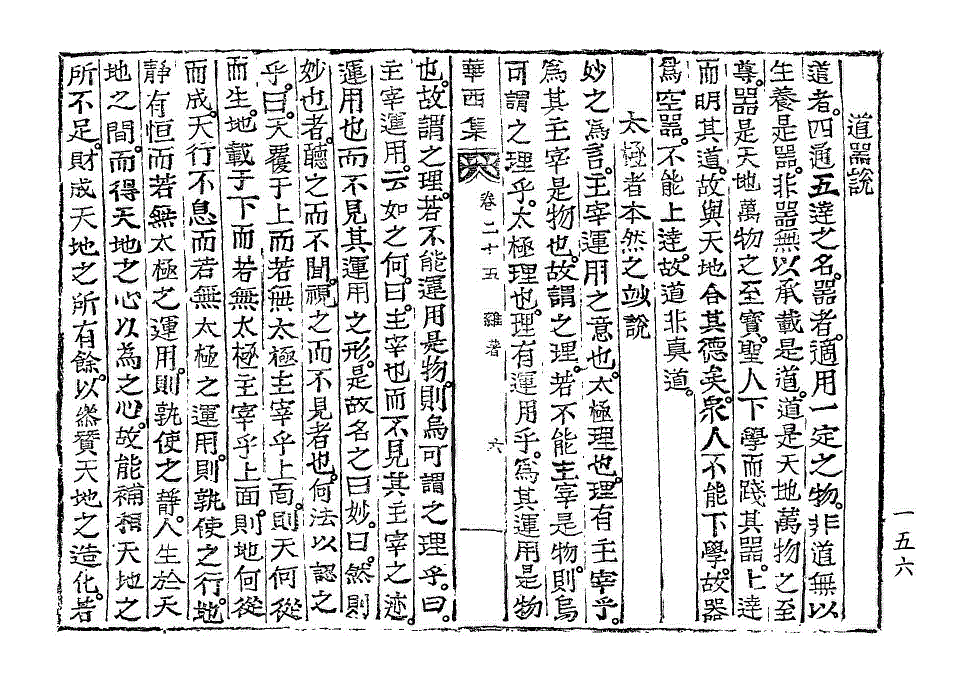 太极者本然之妙说
太极者本然之妙说妙之为言。主宰运用之意也。太极理也。理有主宰乎。为其主宰是物也。故谓之理。若不能主宰是物。则乌可谓之理乎。太极理也。理有运用乎。为其运用是物也。故谓之理。若不能运用是物。则乌可谓之理乎。曰。主宰运用。云如之何。曰。主宰也而不见其主宰之迹。运用也而不见其运用之形。是故名之曰妙。曰。然则妙也者。听之而不闻。视之而不见者也。何法以认之乎。曰。天覆于上而若无太极主宰乎上面。则天何从而生。地载于下而若无太极主宰乎上面。则地何从而成。天行不息而若无太极之运用。则孰使之行。地静有恒而若无太极之运用。则孰使之静。人生于天地之间。而得天地之心以为之心。故能补相天地之所不足。财成天地之所有馀。以参赞天地之造化。若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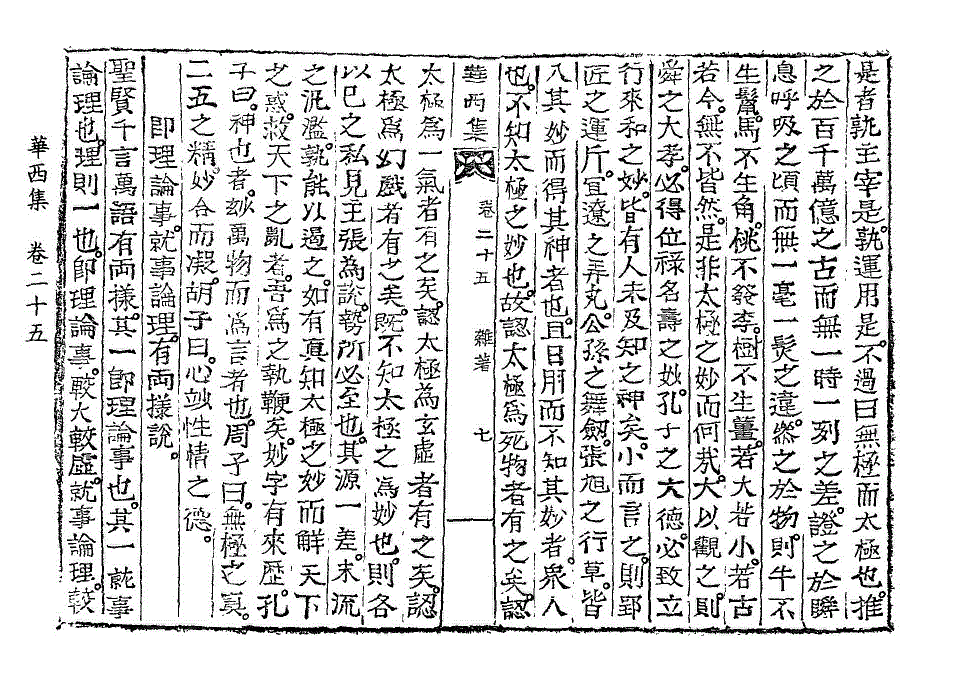 是者孰主宰是。孰运用是。不过曰无极而太极也。推之于百千万亿之古而无一时一刻之差。證之于瞬息呼吸之顷而无一毫一发之违。参之于物。则牛不生鬣。马不生角。桃不发李。树不生姜。若大若小。若古若今。无不皆然。是非太极之妙而何哉。大以观之。则舜之大孝。必得位禄名寿之妙。孔子之大德。必致立行来和之妙。皆有人未及知之神矣。小而言之。则郢匠之运斤。宜辽之弄丸。公孙之舞剑。张旭之行草。皆入其妙而得其神者也。且日用而不知其妙者。众人也。不知太极之妙也。故认太极为死物者有之矣。认太极为一气者有之矣。认太极为玄虚者有之矣。认太极为幻戏者有之矣。既不知太极之为妙也。则各以己之私见主张为说。势所必至也。其源一差。末流之汎滥。孰能以遏之。如有真知太极之妙而解天下之惑。救天下之乱者。吾为之执鞭矣。妙字有来历。孔子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周子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胡子曰。心妙性情之德。
是者孰主宰是。孰运用是。不过曰无极而太极也。推之于百千万亿之古而无一时一刻之差。證之于瞬息呼吸之顷而无一毫一发之违。参之于物。则牛不生鬣。马不生角。桃不发李。树不生姜。若大若小。若古若今。无不皆然。是非太极之妙而何哉。大以观之。则舜之大孝。必得位禄名寿之妙。孔子之大德。必致立行来和之妙。皆有人未及知之神矣。小而言之。则郢匠之运斤。宜辽之弄丸。公孙之舞剑。张旭之行草。皆入其妙而得其神者也。且日用而不知其妙者。众人也。不知太极之妙也。故认太极为死物者有之矣。认太极为一气者有之矣。认太极为玄虚者有之矣。认太极为幻戏者有之矣。既不知太极之为妙也。则各以己之私见主张为说。势所必至也。其源一差。末流之汎滥。孰能以遏之。如有真知太极之妙而解天下之惑。救天下之乱者。吾为之执鞭矣。妙字有来历。孔子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周子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胡子曰。心妙性情之德。即理论事。就事论理。有两㨾说。
圣贤千言万语有两㨾。其一即理论事也。其一就事论理也。理则一也。即理论事。较大较虚。就事论理。较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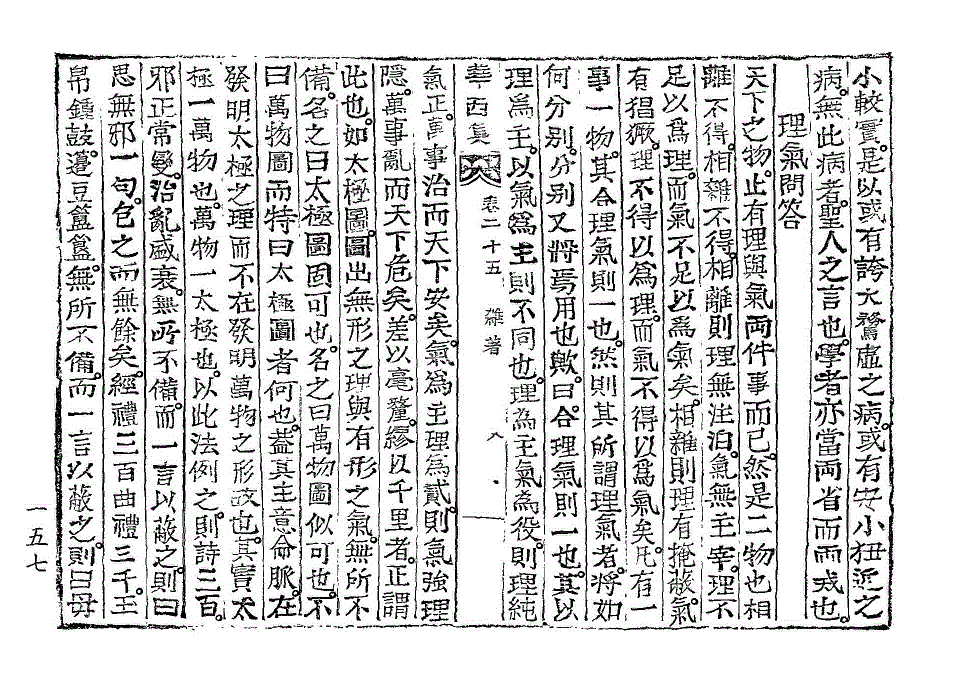 小较实。是以或有誇大惊虚之病。或有安小狃近之病。无此病者。圣人之言也。学者亦当两省而两戒也。
小较实。是以或有誇大惊虚之病。或有安小狃近之病。无此病者。圣人之言也。学者亦当两省而两戒也。理气问答
天下之物。止有理与气两件事而已。然是二物也相离不得。相杂不得。相离则理无注泊。气无主宰。理不足以为理。而气不足以为气矣。相杂则理有掩蔽。气有猖獗。理不得以为理。而气不得以为气矣。凡有一事一物。其合理气则一也。然则其所谓理气者。将如何分别。分别又将焉用也欤。曰。合理气则一也。其以理为主。以气为主则不同也。理为主气为役。则理纯气正。万事治而天下安矣。气为主理为贰。则气强理隐。万事乱而天下危矣。差以毫釐。缪以千里者。正谓此也。如太极图。图出无形之理与有形之气。无所不备。名之曰太极图固可也。名之曰万物图似可也。不曰万物图而特曰太极图者何也。盖其主意命脉。在发明太极之理而不在发明万物之形故也。其实太极一万物也。万物一太极也。以此法例之。则诗三百。邪正常变。治乱盛衰。无所不备。而一言以蔽之。则曰思无邪一句。包之而无馀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玉帛钟鼓。笾豆簠簋。无所不备。而一言以蔽之。则曰毋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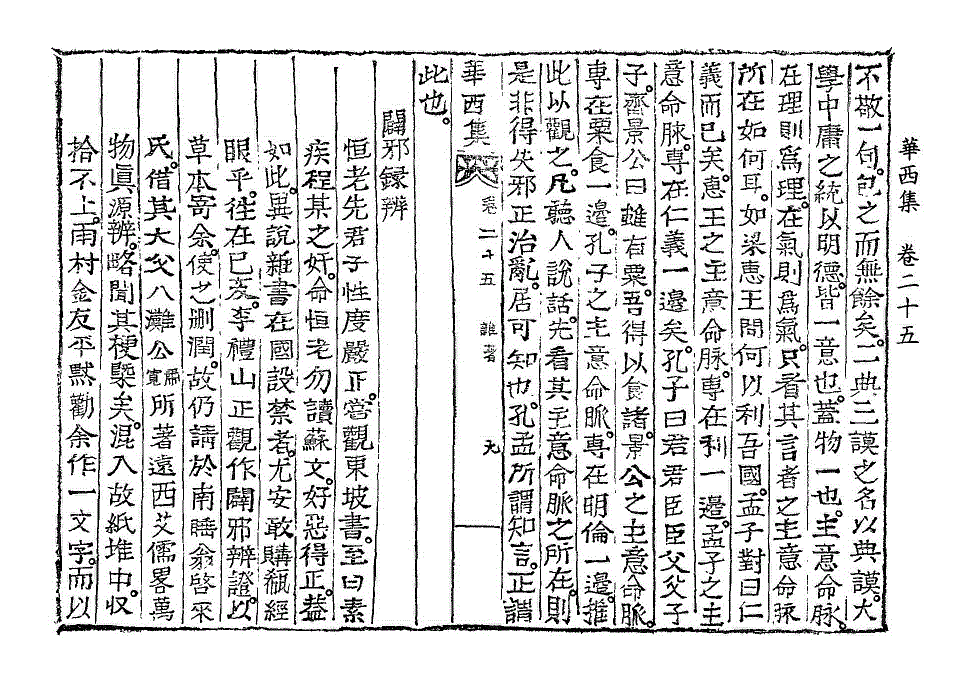 不敬一句。包之而无馀矣。二典三谟之名以典谟。大学中庸之统以明德。皆一意也。盖物一也。主意命脉。在理则为理。在气则为气。只看其言者之主意命脉所在如何耳。如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仁义而已矣。惠王之主意命脉。专在利一边。孟子之主意命脉。专在仁义一边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曰虽有粟。吾得以食诸。景公之主意命脉。专在粟食一边。孔子之主意命脉。专在明伦一边。推此以观之。凡听人说话。先看其主意命脉之所在。则是非得失邪正治乱。居可知也。孔孟所谓知言。正谓此也。
不敬一句。包之而无馀矣。二典三谟之名以典谟。大学中庸之统以明德。皆一意也。盖物一也。主意命脉。在理则为理。在气则为气。只看其言者之主意命脉所在如何耳。如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仁义而已矣。惠王之主意命脉。专在利一边。孟子之主意命脉。专在仁义一边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曰虽有粟。吾得以食诸。景公之主意命脉。专在粟食一边。孔子之主意命脉。专在明伦一边。推此以观之。凡听人说话。先看其主意命脉之所在。则是非得失邪正治乱。居可知也。孔孟所谓知言。正谓此也。辟邪录辨
恒老先君子性度严正。尝观东坡书。至曰素疾程某之奸。命恒老勿读苏文。好恶得正。盖如此。异说杂书在国设禁者。尤安敢购瓻经眼乎。往在己亥。李礼山正观作辟邪辨證。以草本寄余。使之删润。故仍请于南睡翁启来氏。借其大父八滩公(肃宽)所著远西艾儒略万物真源辨。略闻其梗槩矣。混入故纸堆中。收拾不上。雨村金友平默劝余作一文字。而以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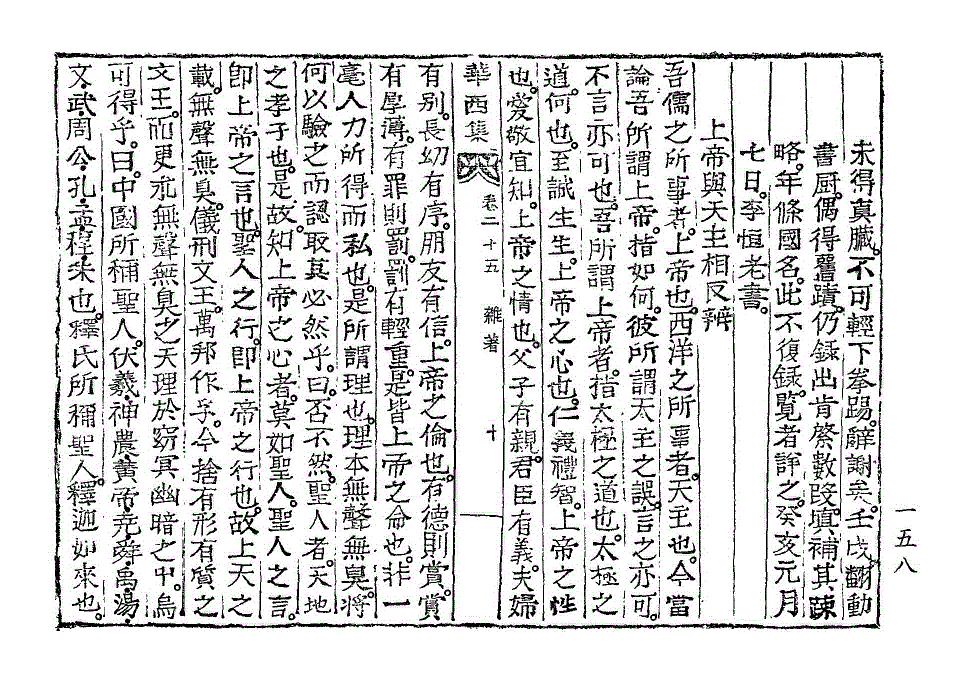 未得真脏。不可轻下拳踢。辞谢矣。壬戌。翻动书厨。偶得旧迹。仍录出肯綮数段。填补其疏略。年条国名。此不复录。览者详之。癸亥元月七日。李恒老书。
未得真脏。不可轻下拳踢。辞谢矣。壬戌。翻动书厨。偶得旧迹。仍录出肯綮数段。填补其疏略。年条国名。此不复录。览者详之。癸亥元月七日。李恒老书。上帝与天主相反辨
吾儒之所事者。上帝也。西洋之所事者。天主也。今当论吾所谓上帝。指如何。彼所谓天主之误。言之亦可。不言亦可也。吾所谓上帝者。指太极之道也。太极之道。何也。至诚生生。上帝之心也。仁义礼智。上帝之性也。爱敬宜知。上帝之情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上帝之伦也。有德则赏。赏有厚薄。有罪则罚。罚有轻重。是皆上帝之命也。非一毫人力所得而私也。是所谓理也。理本无声无臭。将何以验之而认取其必然乎。曰。否不然。圣人者。天地之孝子也。是故。知上帝之心者。莫如圣人。圣人之言。即上帝之言也。圣人之行。即上帝之行也。故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今舍有形有质之文王。而更求无声无臭之天理于窈冥幽暗之中。乌可得乎。曰。中国所称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也。释氏所称圣人。释迦如来也。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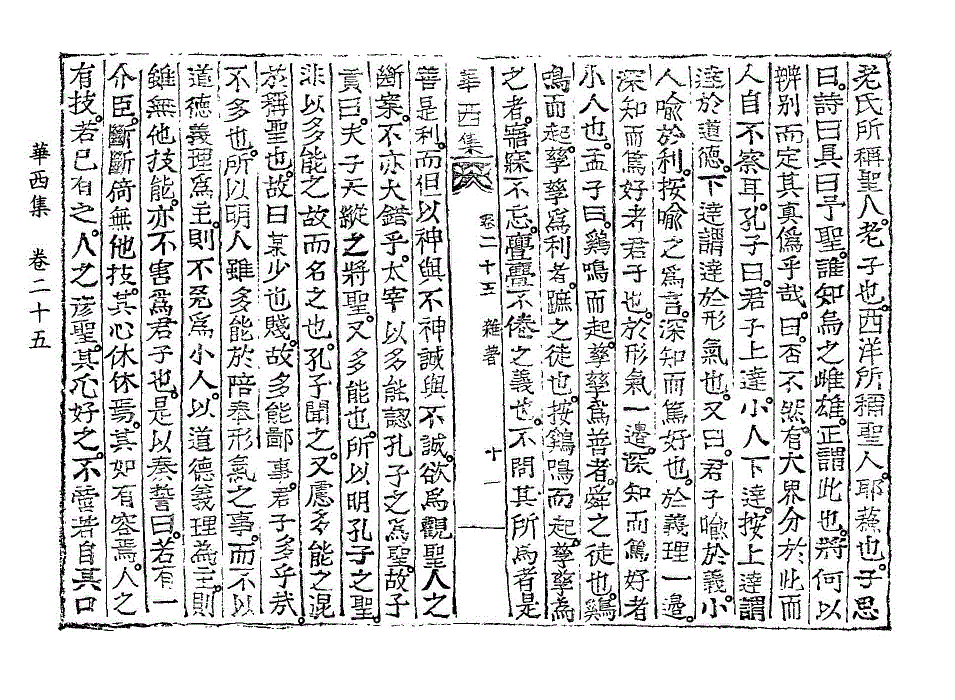 老氏所称圣人。老子也。西洋所称圣人。耶苏也。子思曰。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正谓此也。将何以辨别而定其真伪乎哉。曰。否不然。有大界分于此而人自不察耳。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按上达谓达于道德。下达谓达于形气也。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按喻之为言。深知而笃好也。于义理一边。深知而笃好者君子也。于形气一边。深知而笃好者小人也。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按鸡鸣而起。孳孳为之者。寤寐不忘。亹亹不倦之义也。不问其所为者是善是利。而但以神与不神诚与不诚。欲为观圣人之断案。不亦大错乎。太宰以多能认孔子之为圣。故子贡曰。夫子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所以明孔子之圣。非以多能之故而名之也。孔子闻之。又虑多能之混于称圣也。故曰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明人虽多能于陪奉形气之事。而不以道德义理为主。则不免为小人。以道德义理为主。则虽无他技能。亦不害为君子也。是以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倚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老氏所称圣人。老子也。西洋所称圣人。耶苏也。子思曰。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正谓此也。将何以辨别而定其真伪乎哉。曰。否不然。有大界分于此而人自不察耳。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按上达谓达于道德。下达谓达于形气也。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按喻之为言。深知而笃好也。于义理一边。深知而笃好者君子也。于形气一边。深知而笃好者小人也。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按鸡鸣而起。孳孳为之者。寤寐不忘。亹亹不倦之义也。不问其所为者是善是利。而但以神与不神诚与不诚。欲为观圣人之断案。不亦大错乎。太宰以多能认孔子之为圣。故子贡曰。夫子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所以明孔子之圣。非以多能之故而名之也。孔子闻之。又虑多能之混于称圣也。故曰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明人虽多能于陪奉形气之事。而不以道德义理为主。则不免为小人。以道德义理为主。则虽无他技能。亦不害为君子也。是以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倚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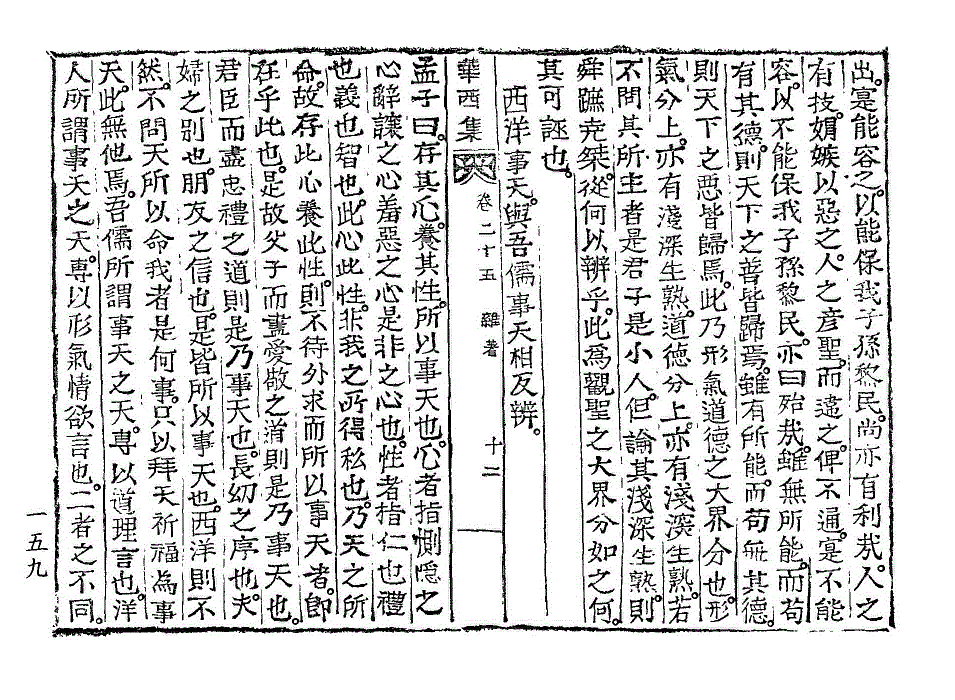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娟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虽无所能。而苟有其德。则天下之善皆归焉。虽有所能。而苟无其德。则天下之恶皆归焉。此乃形气道德之大界分也。形气分上。亦有浅深生熟。道德分上。亦有浅深生熟。若不问其所主者是君子是小人。但论其浅深生熟。则舜蹠尧桀。从何以辨乎。此为观圣之大界分如之何。其可诬也。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娟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虽无所能。而苟有其德。则天下之善皆归焉。虽有所能。而苟无其德。则天下之恶皆归焉。此乃形气道德之大界分也。形气分上。亦有浅深生熟。道德分上。亦有浅深生熟。若不问其所主者是君子是小人。但论其浅深生熟。则舜蹠尧桀。从何以辨乎。此为观圣之大界分如之何。其可诬也。西洋事天。与吾儒事天相反辨。
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心者指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也。性者指仁也礼也义也智也。此心此性。非我之所得私也。乃天之所命。故存此心养此性。则不待外求而所以事天者。即在乎此也。是故父子而尽爱敬之道则是乃事天也。君臣而尽忠礼之道则是乃事天也。长幼之序也。夫妇之别也。朋友之信也。是皆所以事天也。西洋则不然。不问天所以命我者是何事。只以拜天祈福为事天。此无他焉。吾儒所谓事天之天。专以道理言也。洋人所谓事天之天。专以形气情欲言也。二者之不同。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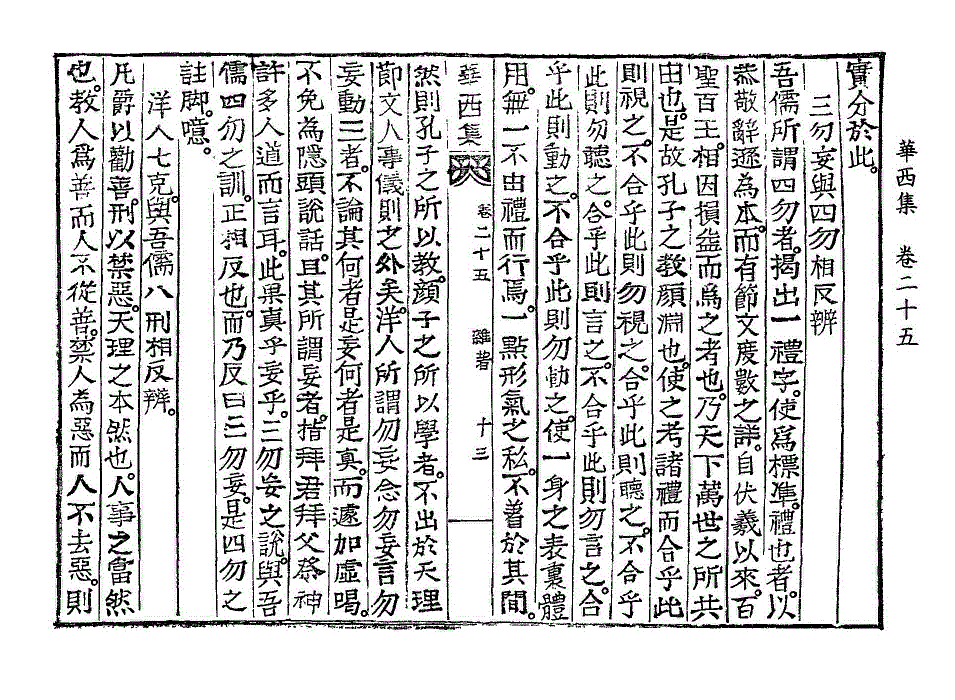 实分于此。
实分于此。三勿妄与四勿相反辨
吾儒所谓四勿者。揭出一礼字。使为标准。礼也者。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自伏羲以来。百圣百王。相因损益而为之者也。乃天下万世之所共由也。是故孔子之教颜渊也。使之考诸礼而合乎此则视之。不合乎此则勿视之。合乎此则听之。不合乎此则勿听之。合乎此则言之。不合乎此则勿言之。合乎此则动之。不合乎此则勿动之。使一身之表里体用。无一不由礼而行焉。一点形气之私。不着于其间。然则孔子之所以教。颜子之所以学者。不出于天理节文人事仪则之外矣。洋人所谓勿妄念勿妄言勿妄动三者。不论其何者是妄何者是真。而遽加虚喝。不免为隐头说话。且其所谓妄者。指拜君拜父祭神许多人道而言耳。此果真乎妄乎。三勿妄之说。与吾儒四勿之训。正相反也。而乃反曰三勿妄。是四勿之注脚。噫。
洋人七克。与吾儒八刑相反辨。
凡爵以劝善。刑以禁恶。天理之本然也。人事之当然也。教人为善而人不从善。禁人为恶而人不去恶。则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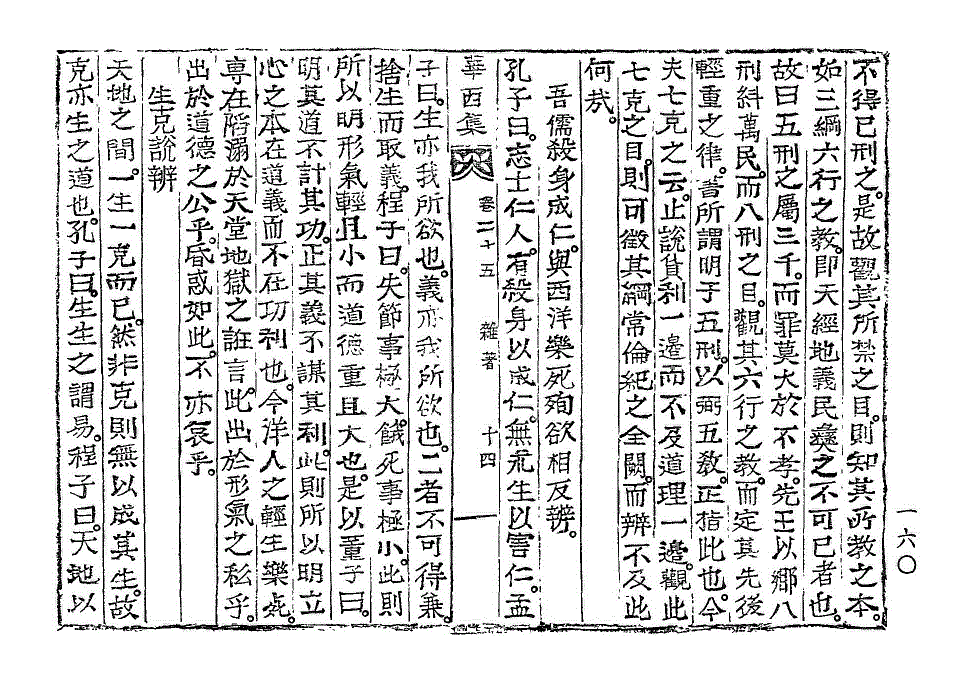 不得已刑之。是故观其所禁之目。则知其所教之本。如三纲六行之教。即天经地义民彝之不可已者也。故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先王以乡八刑纠万民。而八刑之目。观其六行之教。而定其先后轻重之律。书所谓明子五刑。以弼五教。正指此也。今夫七克之云。止说货利一边而不及道理一边。观此七克之目。则可徵其纲常伦纪之全阙。而辨不及此何哉。
不得已刑之。是故观其所禁之目。则知其所教之本。如三纲六行之教。即天经地义民彝之不可已者也。故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先王以乡八刑纠万民。而八刑之目。观其六行之教。而定其先后轻重之律。书所谓明子五刑。以弼五教。正指此也。今夫七克之云。止说货利一边而不及道理一边。观此七克之目。则可徵其纲常伦纪之全阙。而辨不及此何哉。吾儒杀身成仁。与西洋乐死殉欲相反辨。
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程子曰。失节事极大。饿死事极小。此则所以明形气轻且小而道德重且大也。是以董子曰。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此则所以明立心之本在道义而不在功利也。今洋人之轻生乐死。专在陷溺于天堂地狱之诳言。此出于形气之私乎。出于道德之公乎。昏惑如此。不亦哀乎。
生克说辨
天地之间。一生一克而已。然非克则无以成其生。故克亦生之道也。孔子曰。生生之谓易。程子曰。天地以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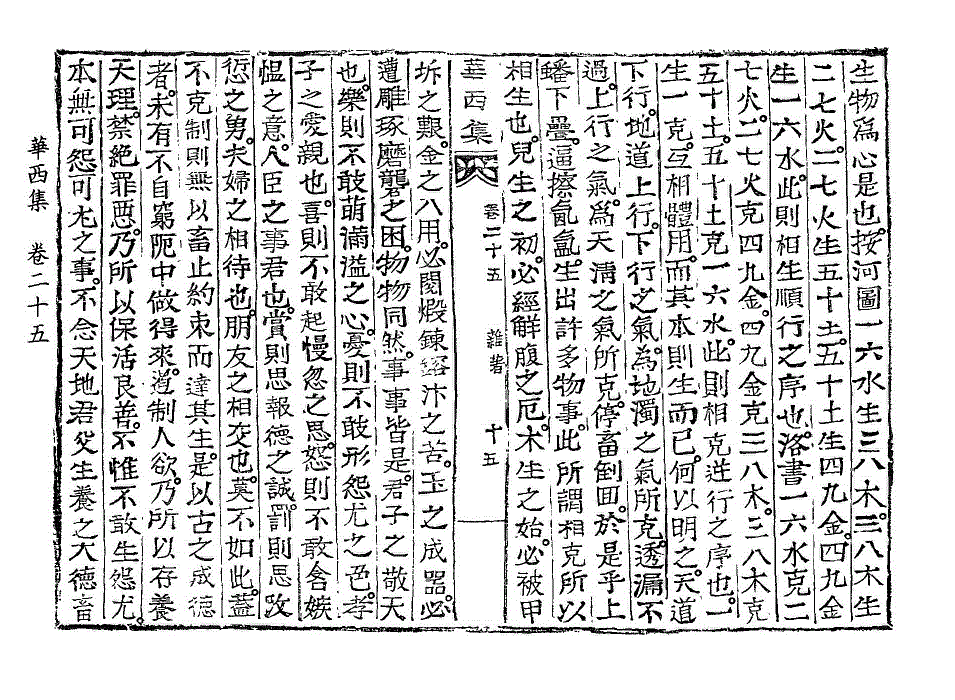 生物为心是也。按河图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生一六水。此则相生顺行之序也。洛书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五十土。五十土克一六水。此则相克逆行之序也。一生一克。互相体用。而其本则生而已。何以明之。天道下行。地道上行。下行之气。为地浊之气所克。透漏不过。上行之气。为天清之气所克。停畜倒回。于是乎上蟠下叠。逼擦氤氲。生出许多物事。此所谓相克所以相生也。儿生之初。必经解腹之厄。木生之始。必被甲坼之艰。金之八用。必阅煅鍊镕汁之苦。玉之成器。必遭雕琢磨砻之困。物物同然。事事皆是。君子之敬天也。乐则不敢萌满溢之心。忧则不敢形怨尤之色。孝子之爱亲也。喜则不敢起慢忽之思。怒则不敢含嫉愠之意。人臣之事君也。赏则思报德之诚。罚则思改愆之勇。夫妇之相待也。朋友之相交也。莫不如此。盖不克制则无以畜止约束而达其生。是以古之成德者。未有不自穷阨中做得来。遏制人欲。乃所以存养天理。禁绝罪恶。乃所以保活良善。不惟不敢生怨尤。本无可怨可尤之事。不念天地君父生养之大德畜
生物为心是也。按河图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生一六水。此则相生顺行之序也。洛书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五十土。五十土克一六水。此则相克逆行之序也。一生一克。互相体用。而其本则生而已。何以明之。天道下行。地道上行。下行之气。为地浊之气所克。透漏不过。上行之气。为天清之气所克。停畜倒回。于是乎上蟠下叠。逼擦氤氲。生出许多物事。此所谓相克所以相生也。儿生之初。必经解腹之厄。木生之始。必被甲坼之艰。金之八用。必阅煅鍊镕汁之苦。玉之成器。必遭雕琢磨砻之困。物物同然。事事皆是。君子之敬天也。乐则不敢萌满溢之心。忧则不敢形怨尤之色。孝子之爱亲也。喜则不敢起慢忽之思。怒则不敢含嫉愠之意。人臣之事君也。赏则思报德之诚。罚则思改愆之勇。夫妇之相待也。朋友之相交也。莫不如此。盖不克制则无以畜止约束而达其生。是以古之成德者。未有不自穷阨中做得来。遏制人欲。乃所以存养天理。禁绝罪恶。乃所以保活良善。不惟不敢生怨尤。本无可怨可尤之事。不念天地君父生养之大德畜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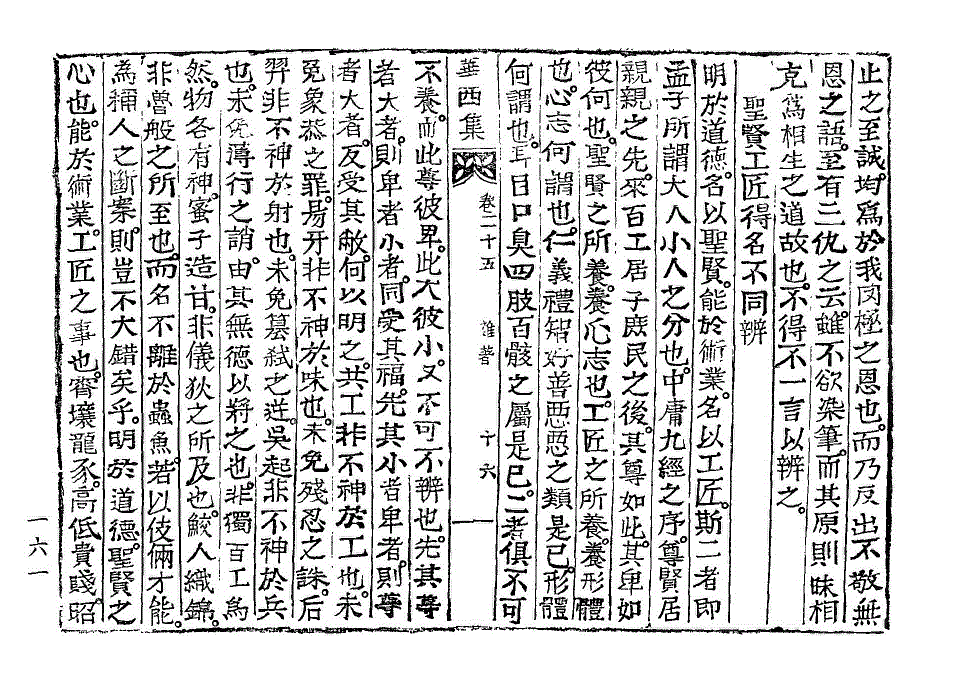 止之至诚。均为于我罔极之恩也。而乃反出不敬无恩之语。至有三仇之云。虽不欲染笔。而其原则昧相克为相生之道故也。不得不一言以辨之。
止之至诚。均为于我罔极之恩也。而乃反出不敬无恩之语。至有三仇之云。虽不欲染笔。而其原则昧相克为相生之道故也。不得不一言以辨之。圣贤工匠得名不同辨
明于道德。名以圣贤。能于术业。名以工匠。斯二者即孟子所谓大人小人之分也。中庸九经之序。尊贤居亲亲之先。来百工居子庶民之后。其尊如此。其卑如彼何也。圣贤之所养。养心志也。工匠之所养。养形体也。心志何谓也。仁义礼智好善恶恶之类是已。形体何谓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属是已。二者俱不可不养。而此尊彼卑。此大彼小。又不可不辨也。先其尊者大者。则卑者小者。同受其福。先其小者卑者。则尊者大者。反受其敝。何以明之。共工非不神于工也。未免象恭之罪。易牙非不神于味也。未免残忍之诛。后羿非不神于射也。未免篡弑之逆。吴起非不神于兵也。未免薄行之诮。由其无德以将之也。非独百工为然。物各有神。蜜子造甘。非仪狄之所及也。鲛人织锦。非鲁般之所至也。而名不离于虫鱼。若以伎俩才能。为称人之断案。则岂不大错矣乎。明于道德。圣贤之心也。能于术业。工匠之事也。霄壤龙豕。高低贵贱。昭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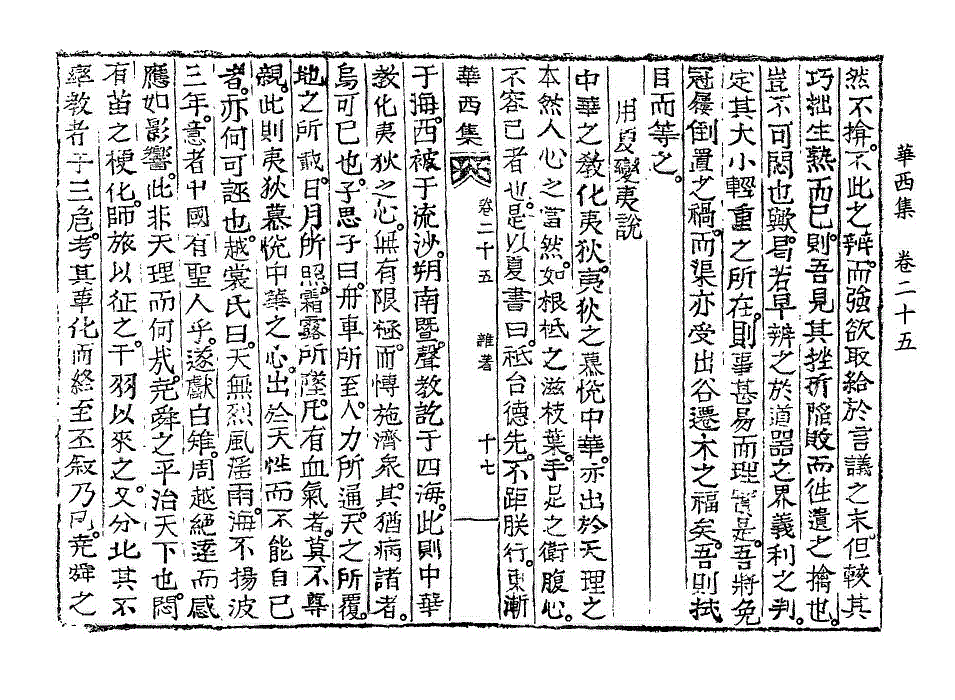 然不掩。不此之辨。而强欲取给于言议之末。但较其巧拙生熟而已。则吾见其挫折陷败而往遗之擒也。岂不可闷也欤。曷若早辨之于道器之界义利之判。定其大小轻重之所在。则事甚易而理实是。吾将免冠屦倒置之祸。而渠亦受出谷迁木之福矣。吾则拭目而等之。
然不掩。不此之辨。而强欲取给于言议之末。但较其巧拙生熟而已。则吾见其挫折陷败而往遗之擒也。岂不可闷也欤。曷若早辨之于道器之界义利之判。定其大小轻重之所在。则事甚易而理实是。吾将免冠屦倒置之祸。而渠亦受出谷迁木之福矣。吾则拭目而等之。用夏变夷说
中华之教化夷狄。夷狄之慕悦中华。亦出于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当然。如根柢之滋枝叶。手足之卫腹心。不容已者也。是以夏书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此则中华教化夷狄之心。无有限极。而博施济众。其犹病诸者。乌可已也。子思子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则夷狄慕悦中华之心。出于天性而不能自已者。亦何可诬也。越裳氏曰。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意者中国有圣人乎。遂献白雉。周越绝远而感应如影响。此非天理而何哉。尧舜之平治天下也。闷有苗之梗化。师旅以征之。干羽以来之。又分北其不率教者于三危。考其革化而终至丕叙乃已。尧舜之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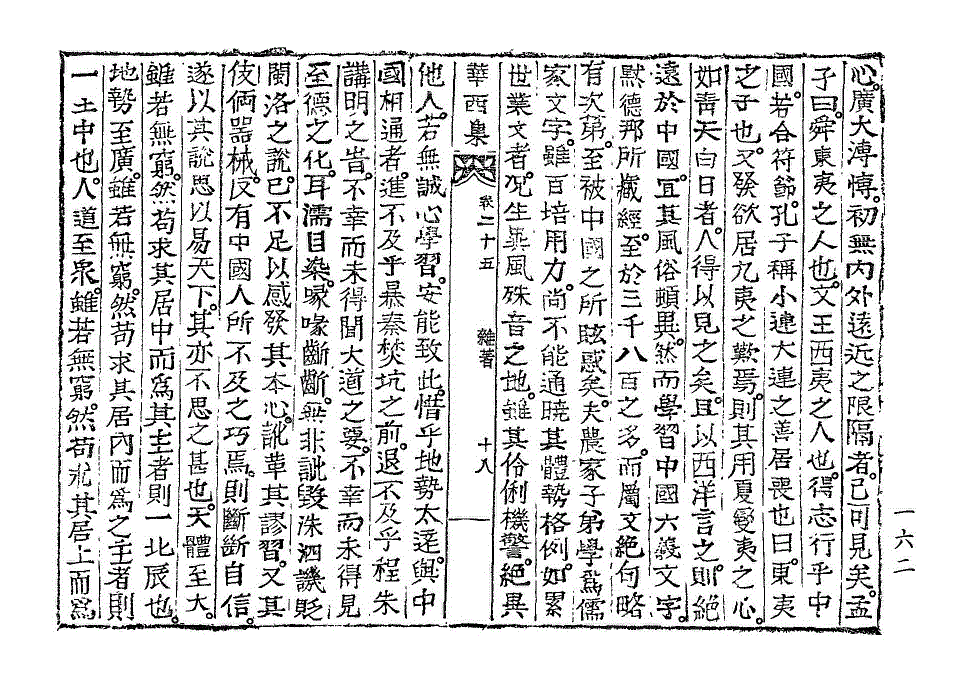 心。广大溥博。初无内外远近之限隔者。已可见矣。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孔子称小连大连之善居丧也曰。东夷之子也。又发欲居九夷之叹焉。则其用夏变夷之心。如青天白日者。人得以见之矣。且以西洋言之。则绝远于中国。宜其风俗顿异。然而学习中国六义文字。默德那所藏经。至于三千八百之多。而属文绝句略有次第。至被中国之所眩惑矣。夫农家子弟学为儒家文字。虽百培用力。尚不能通晓其体势格例。如累世业文者。况生异风殊音之地。虽其伶俐机警。绝异他人。若无诚心学习。安能致此。惜乎地势太远。与中国相通者。进不及乎暴秦焚坑之前。退不及乎程朱讲明之时。不幸而未得闻大道之要。不幸而未得见至德之化。耳濡目染。喙喙龂龂。无非訾毁洙泗讥贬闽洛之说。已不足以感发其本心。讹革其谬习。又其伎俩器械。反有中国人所不及之巧焉。则断断自信。遂以其说思以易天下。其亦不思之甚也。天体至大。虽若无穷。然苟求其居中而为其主者则一北辰也。地势至广。虽若无穷。然苟求其居内而为之主者则一土中也。人道至众。虽若无穷。然苟求其居上而为
心。广大溥博。初无内外远近之限隔者。已可见矣。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孔子称小连大连之善居丧也曰。东夷之子也。又发欲居九夷之叹焉。则其用夏变夷之心。如青天白日者。人得以见之矣。且以西洋言之。则绝远于中国。宜其风俗顿异。然而学习中国六义文字。默德那所藏经。至于三千八百之多。而属文绝句略有次第。至被中国之所眩惑矣。夫农家子弟学为儒家文字。虽百培用力。尚不能通晓其体势格例。如累世业文者。况生异风殊音之地。虽其伶俐机警。绝异他人。若无诚心学习。安能致此。惜乎地势太远。与中国相通者。进不及乎暴秦焚坑之前。退不及乎程朱讲明之时。不幸而未得闻大道之要。不幸而未得见至德之化。耳濡目染。喙喙龂龂。无非訾毁洙泗讥贬闽洛之说。已不足以感发其本心。讹革其谬习。又其伎俩器械。反有中国人所不及之巧焉。则断断自信。遂以其说思以易天下。其亦不思之甚也。天体至大。虽若无穷。然苟求其居中而为其主者则一北辰也。地势至广。虽若无穷。然苟求其居内而为之主者则一土中也。人道至众。虽若无穷。然苟求其居上而为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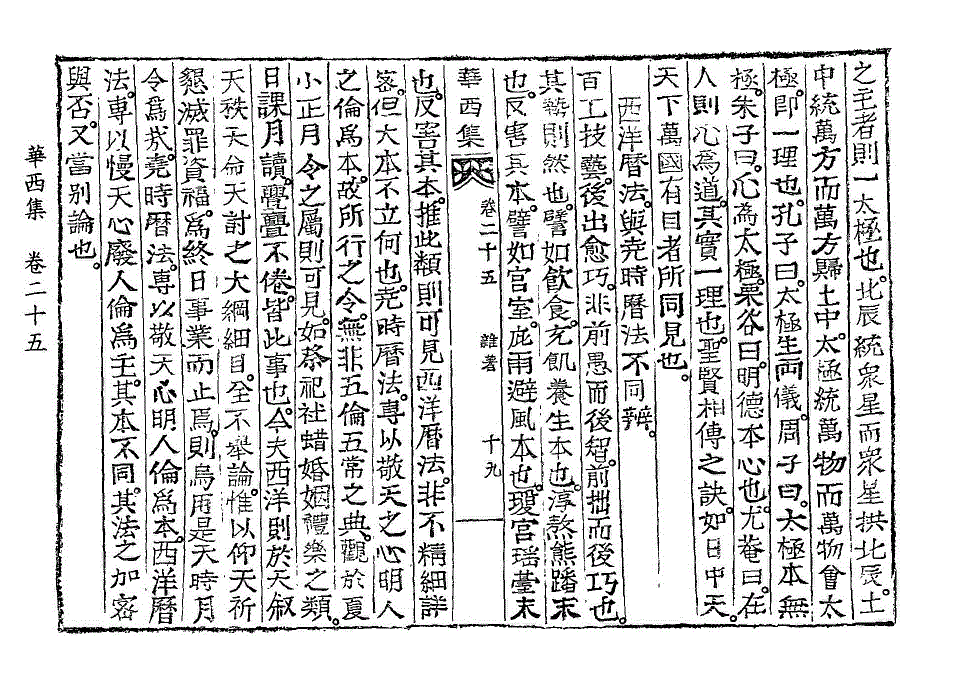 之主者则一太极也。北辰统众星而众星拱北辰。土中统万方而万方归土中。太极统万物而万物会太极。即一理也。孔子曰。太极生两仪。周子曰。太极本无极。朱子曰。心为太极。栗谷曰。明德本心也。尤庵曰。在人则心为道。其实一理也。圣贤相传之诀。如日中天。天下万国有目者所同见也。
之主者则一太极也。北辰统众星而众星拱北辰。土中统万方而万方归土中。太极统万物而万物会太极。即一理也。孔子曰。太极生两仪。周子曰。太极本无极。朱子曰。心为太极。栗谷曰。明德本心也。尤庵曰。在人则心为道。其实一理也。圣贤相传之诀。如日中天。天下万国有目者所同见也。西洋历法。与尧时历法不同辨。
百工技艺。后出愈巧。非前愚而后智。前拙而后巧也。其势则然也。譬如饮食。充饥养生本也。淳熬熊蹯末也。反害其本。譬如宫室。庇雨避风本也。琼宫瑶台末也。反害其本。推此类则可见西洋历法。非不精细详密。但大本不立何也。尧时历法。专以敬天之心明人之伦为本。故所行之令。无非五伦五常之典。观于夏小正月令之属则可见。如祭祀社蜡婚姻礼乐之类。日课月读。亹亹不倦。皆此事也。今夫西洋则于天叙天秩天命天讨之大纲细目。全不举论。惟以仰天祈恳灭罪资福。为终日事业而止焉。则乌用是天时月令为哉。尧时历法。专以敬天心明人伦为本。西洋历法。专以慢天心废人伦为主。其本不同。其法之加密与否。又当别论也。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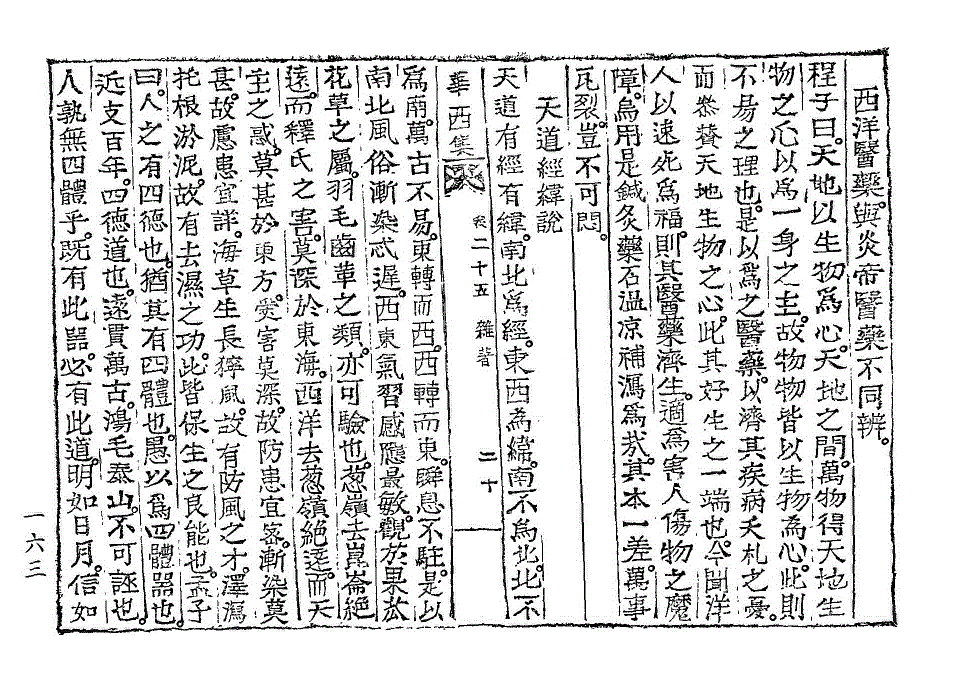 西洋医药。与炎帝医药不同辨。
西洋医药。与炎帝医药不同辨。程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间。万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一身之主。故物物皆以生物为心。此则不易之理也。是以为之医药。以济其疾病夭札之忧。而参赞天地生物之心。此其好生之一端也。今闻洋人以速死为福。则其医药济生。适为害人伤物之魔障。乌用是针炙药石温凉补泻为哉。其本一差。万事瓦裂。岂不可闷。
天道经纬说
天道有经有纬。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南不为北。北不为南。万古不易。东转而西。西转而东。瞬息不驻。是以南北风俗渐染忒迟。西东气习感应最敏。观于果菰花草之属。羽毛齿革之类。亦可验也。葱岭去昆崙绝远。而释氏之害。莫深于东海。西洋去葱岭绝远。而天主之惑。莫甚于东方。受害莫深。故防患宜密。渐染莫甚。故虑患宜详。海草生长狞风。故有防风之才。泽泻托根淤泥。故有去湿之功。此皆保生之良能也。孟子曰。人之有四德也。犹其有四体也。愚以为四体器也。近支百年。四德道也。远贯万古。鸿毛泰山。不可诬也。人孰无四体乎。既有此器。必有此道。明如日月。信如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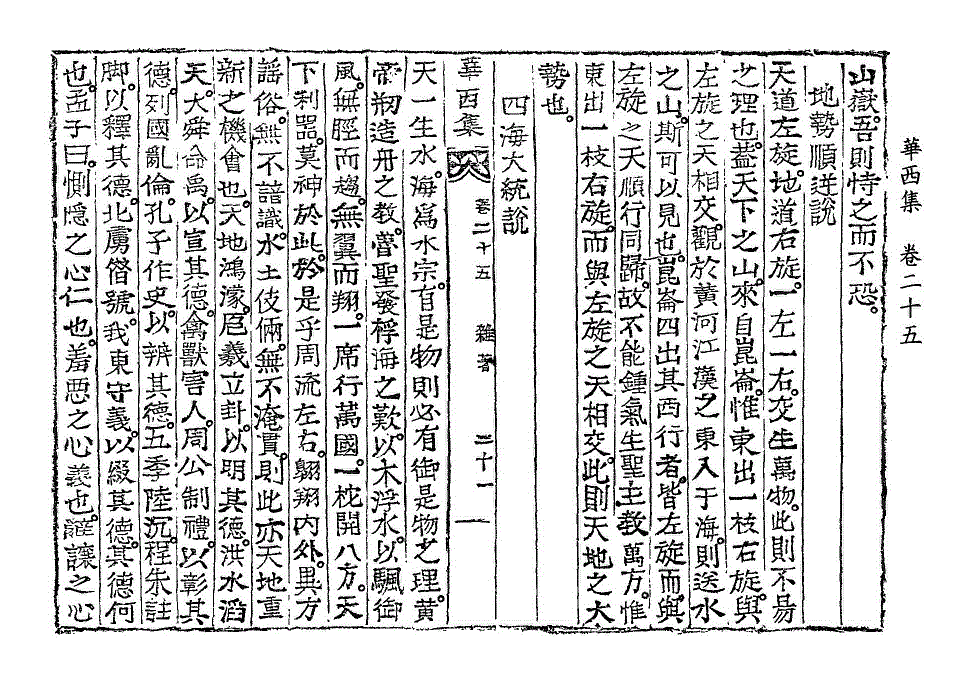 山岳。吾则恃之而不恐。
山岳。吾则恃之而不恐。地势顺逆说
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一左一右。交生万物。此则不易之理也。盖天下之山。来自昆崙。惟东出一枝右旋。与左旋之天相交。观于黄河江汉之东入于海。则送水之山。斯可以见也。昆崙四出其西行者。皆左旋。而与左旋之天顺行同归。故不能钟气生圣主教万方。惟东出一枝右旋。而与左旋之天相交。此则天地之大势也。
四海大统说
天一生水。海为水宗。有是物则必有御是物之理。黄帝刱造舟之教。鲁圣发桴海之叹。以木浮水。以帆御风。无胫而趋。无翼而翔。一席行万国。一柁开八方。天下利器。莫神于此。于是乎周流左右。翱翔内外。异方谣俗。无不谙识。水土伎俩。无不淹贯。则此亦天地重新之机会也。天地鸿濛。庖羲立卦。以明其德。洪水滔天。大舜命禹。以宣其德。禽兽害人。周公制礼。以彰其德。列国乱伦。孔子作史。以辨其德。五季陆沉。程朱注脚。以释其德。北虏僭号。我东守义。以缀其德。其德何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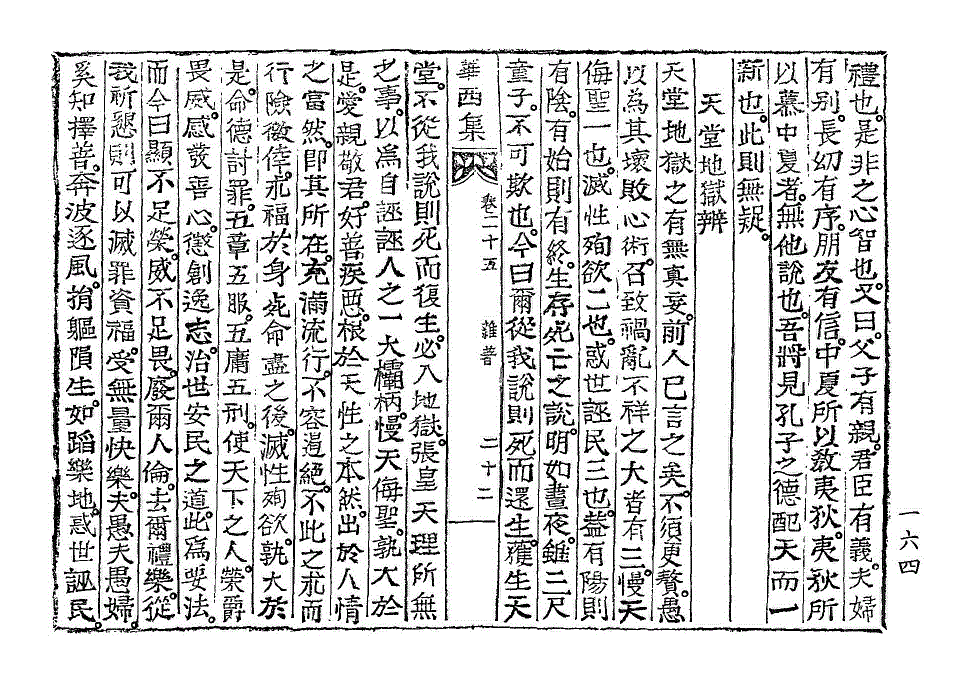 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又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夏所以教夷狄。夷狄所以慕中夏者。无他说也。吾将见孔子之德配天而一新也。此则无疑。
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又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夏所以教夷狄。夷狄所以慕中夏者。无他说也。吾将见孔子之德配天而一新也。此则无疑。天堂地狱辨
天堂地狱之有无真妄。前人已言之矣。不须更赘。愚以为其坏败心术。召致祸乱不祥之大者有三。慢天侮圣一也。灭性殉欲二也。惑世诬民三也。盖有阳则有阴。有始则有终。生存死亡之说。明如昼夜。虽三尺童子。不可欺也。今曰尔从我说则死而还生。获生天堂。不从我说则死而复生。必入地狱。张皇天理所无之事。以为自诬诬人之一大把柄。慢天侮圣。孰大于是。爱亲敬君。好善疾恶。根于天性之本然。出于人情之当然。即其所在。充满流行。不容遏绝。不此之求而行险徼倖。求福于身死命尽之后。灭性殉欲。孰大于是。命德讨罪。五章五服。五庸五刑。使天下之人。荣爵畏威。感发善心。惩创逸志。治世安民之道。此为要法。而今曰显不足荣。威不足畏。废尔人伦。去尔礼乐。从我祈恳则可以灭罪资福。受无量快乐。夫愚夫愚妇。奚知择善。奔波逐风。捐躯陨生。如蹈乐地。惑世诬民。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5H 页
 孰急于是。仁人君子坐视其必然之祸。不一言以辨之乎。辨之如何。福善祸恶。天道也。其原在天。明善惩恶。圣教也。其说在方册。喜善怒恶。人情也。体验在身。熟复此三者。必无不得之理。孟子曰。作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夫岂无理而圣人言之。又曰。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愚以为圣人之道复明。则岂徒中国安。海外万国举安。吾言无疑。○堂狱之源。出自葱岭。汎滥四流。近西诸国。受毒尤深。其势固然。但葱岭之害。犹有限节。绝男女禁鱼肉。戒曲蘖削髭发。见行许多受戒然后。始名为比丘。其害尚浅。洋说不然。男女不必绝。鱼肉不必禁。曲蘖不必戒。髭发不必削。惟心之邪正勿问。人之恩雠两忘。般乐怠傲。人欲不期滋而日滋。天理不期消而日消。其浸淫薄蚀。充塞仁义之祸。反有甚于薙发烧臂之流。为吾学者当如何。猛省而疾治之也。苟求所差之时。则其来甚远。道家养生。参同鍊气。庄列匿名之类。皆因缘人物好生恶死之情。弄假成真。想无为有。遂作千古正学无穷之病。岂不可闷然。病剧则必生已病之药。害切则必有去害之道。此则天地生物之心也。
孰急于是。仁人君子坐视其必然之祸。不一言以辨之乎。辨之如何。福善祸恶。天道也。其原在天。明善惩恶。圣教也。其说在方册。喜善怒恶。人情也。体验在身。熟复此三者。必无不得之理。孟子曰。作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夫岂无理而圣人言之。又曰。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愚以为圣人之道复明。则岂徒中国安。海外万国举安。吾言无疑。○堂狱之源。出自葱岭。汎滥四流。近西诸国。受毒尤深。其势固然。但葱岭之害。犹有限节。绝男女禁鱼肉。戒曲蘖削髭发。见行许多受戒然后。始名为比丘。其害尚浅。洋说不然。男女不必绝。鱼肉不必禁。曲蘖不必戒。髭发不必削。惟心之邪正勿问。人之恩雠两忘。般乐怠傲。人欲不期滋而日滋。天理不期消而日消。其浸淫薄蚀。充塞仁义之祸。反有甚于薙发烧臂之流。为吾学者当如何。猛省而疾治之也。苟求所差之时。则其来甚远。道家养生。参同鍊气。庄列匿名之类。皆因缘人物好生恶死之情。弄假成真。想无为有。遂作千古正学无穷之病。岂不可闷然。病剧则必生已病之药。害切则必有去害之道。此则天地生物之心也。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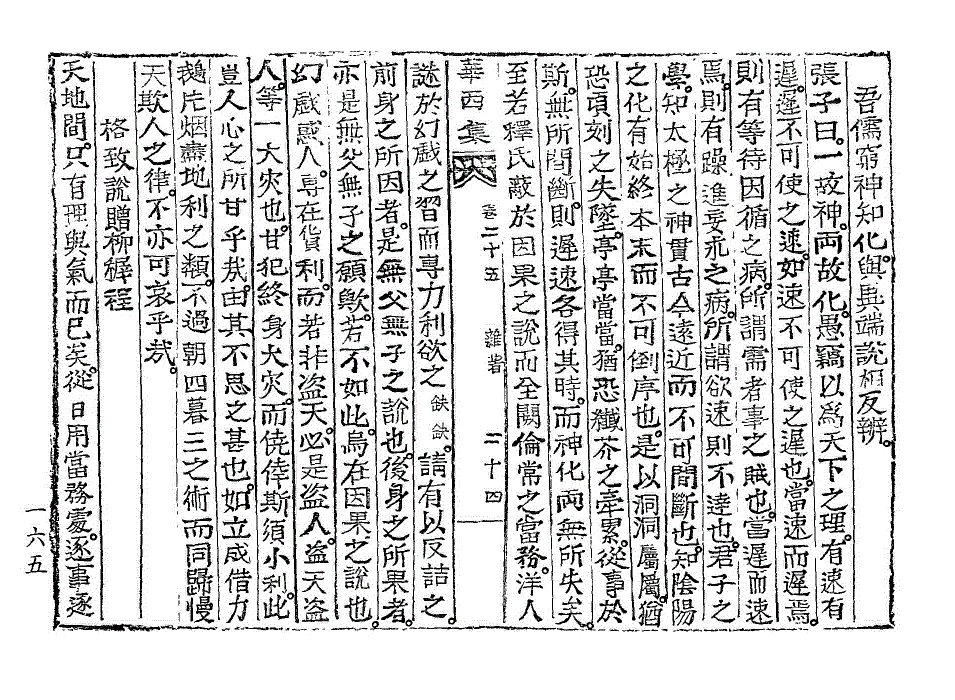 吾儒穷神知化。与异端说相反辨。
吾儒穷神知化。与异端说相反辨。张子曰。一故神。两故化。愚窃以为天下之理。有速有迟。迟不可使之速。如速不可使之迟也。当速而迟焉。则有等待因循之病。所谓需者事之贼也。当迟而速焉。则有躁进妄求之病。所谓欲速则不达也。君子之学。知太极之神贯古今远近而不可间断也。知阴阳之化有始终本末而不可倒序也。是以洞洞属属。犹恐顷刻之失坠。亭亭当当。犹恐纤芥之牵累。从事于斯。无所间断。则迟速各得其时。而神化两无所失矣。至若释氏蔽于因果之说而全阙伦常之当务。洋人谜于幻戏之习而专力利欲之(缺缺。)请有以反诘之。前身之所因者。是无父无子之说也。后身之所果者。亦是无父无子之愿欤。若不如此。乌在因果之说也。幻戏惑人。专在货利。而若非盗天。必是盗人。盗天盗人。等一大灾也。甘犯终身大灾。而侥倖斯须小利。此岂人心之所甘乎哉。由其不思之甚也。如立成借力鹅片烟尽地利之类。不过朝四暮三之术而同归慢天欺人之律。不亦可哀乎哉。
格致说赠柳稚程
天地间。只有理与气而已矣。从日用当务处。逐事逐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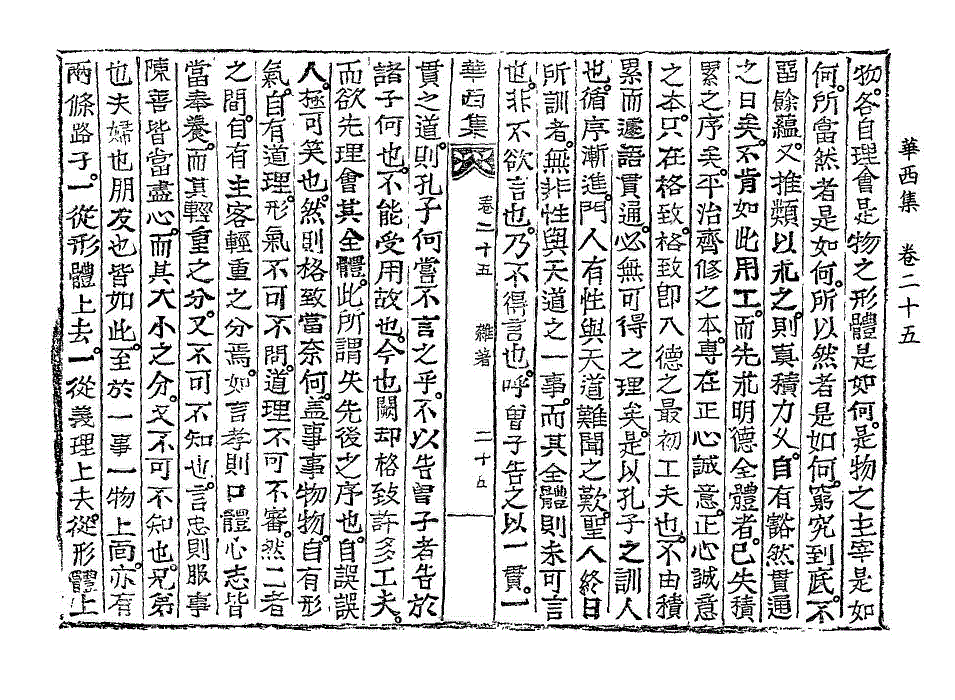 物。各自理会是物之形体是如何。是物之主宰是如何。所当然者是如何。所以然者是如何。穷究到底。不留馀蕴。又推类以求之。则真积力久。自有豁然贯通之日矣。不肯如此用工。而先求明德全体者。已失积累之序矣。平治齐修之本。专在正心诚意。正心诚意之本。只在格致。格致即入德之最初工夫也。不由积累而遽语贯通。必无可得之理矣。是以孔子之训人也。循序渐进。门人有性与天道难闻之叹。圣人终日所训者。无非性与天道之一事。而其全体则未可言也。非不欲言也。乃不得言也。呼曾子告之以一贯。一贯之道。则孔子何尝不言之乎。不以告曾子者告于诸子何也。不能受用故也。今也阙却格致许多工夫。而欲先理会其全体。此所谓失先后之序也。自误误人。极可笑也。然则格致当奈何。盖事事物物。自有形气。自有道理。形气不可不问。道理不可不审。然二者之间。自有主客轻重之分焉。如言孝则口体心志皆当奉养。而其轻重之分。又不可不知也。言忠则服事陈善皆当尽心。而其大小之分。又不可不知也。兄弟也夫妇也朋友也皆如此。至于一事一物上面。亦有两条路子。一从形体上去。一从义理上去。从形体上
物。各自理会是物之形体是如何。是物之主宰是如何。所当然者是如何。所以然者是如何。穷究到底。不留馀蕴。又推类以求之。则真积力久。自有豁然贯通之日矣。不肯如此用工。而先求明德全体者。已失积累之序矣。平治齐修之本。专在正心诚意。正心诚意之本。只在格致。格致即入德之最初工夫也。不由积累而遽语贯通。必无可得之理矣。是以孔子之训人也。循序渐进。门人有性与天道难闻之叹。圣人终日所训者。无非性与天道之一事。而其全体则未可言也。非不欲言也。乃不得言也。呼曾子告之以一贯。一贯之道。则孔子何尝不言之乎。不以告曾子者告于诸子何也。不能受用故也。今也阙却格致许多工夫。而欲先理会其全体。此所谓失先后之序也。自误误人。极可笑也。然则格致当奈何。盖事事物物。自有形气。自有道理。形气不可不问。道理不可不审。然二者之间。自有主客轻重之分焉。如言孝则口体心志皆当奉养。而其轻重之分。又不可不知也。言忠则服事陈善皆当尽心。而其大小之分。又不可不知也。兄弟也夫妇也朋友也皆如此。至于一事一物上面。亦有两条路子。一从形体上去。一从义理上去。从形体上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6L 页
 去则路穷而不通。从义理上去则路通而不塞。如饮食之膏粱刍豢形体也。充饥养生主宰也。衣服之绮纨锦绣形体也。掩体正容主宰也。朱子所谓砚上也有天理人欲。墨上也有天理人欲。正谓此也。不从一事一物上。各分其两路界分。却从全体上面。认取路脉。微妙眩幻。不唤东作西者。几希矣。从今以往。当依大学次第。着实下工。不可复如前颠倒。徒劳而无功也。癸亥元月二十五日晓。
去则路穷而不通。从义理上去则路通而不塞。如饮食之膏粱刍豢形体也。充饥养生主宰也。衣服之绮纨锦绣形体也。掩体正容主宰也。朱子所谓砚上也有天理人欲。墨上也有天理人欲。正谓此也。不从一事一物上。各分其两路界分。却从全体上面。认取路脉。微妙眩幻。不唤东作西者。几希矣。从今以往。当依大学次第。着实下工。不可复如前颠倒。徒劳而无功也。癸亥元月二十五日晓。五伦一阴阳说
周子曰。五行一阴阳也。盖曰火木土阳也。水金阴也。愚亦曰五伦一阴阳也。阴生阳阳生阴。即父子之续也。阳统阴阴承阳。即君臣之义也。阳配阴阴从阳。即夫妇之别也。阳先阴阴后阳。即兄弟之序也。阳与阳相求。阴与阴相应。即朋友之信也。此是天伦。非人之所得以私也。故曰天叙天秩。
在物为理。处物为义说。
愚按物有物之宜。即在物之理也。我有应物之宜。即在我之义也。物虽有理而处之失宜则非义也。在我者虽无私心而处之不合于物理则亦非义也。此所谓合内外之道也。比之饮食。则甘酸辛咸之理在饮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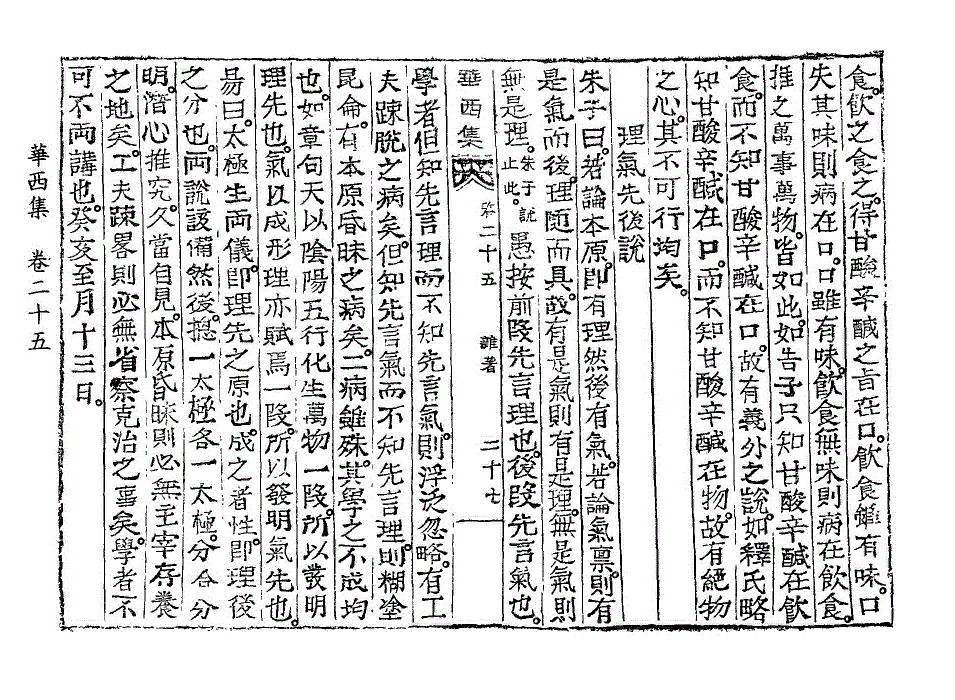 食。饮之食之。得甘酸辛咸之旨在口。饮食虽有味。口失其味则病在口。口虽有味。饮食无味则病在饮食。推之万事万物。皆如此。如告子只知甘酸辛咸在饮食。而不知甘酸辛咸在口。故有义外之说。如释氏略知甘酸辛咸在口。而不知甘酸辛咸在物。故有绝物之心。其不可行均矣。
食。饮之食之。得甘酸辛咸之旨在口。饮食虽有味。口失其味则病在口。口虽有味。饮食无味则病在饮食。推之万事万物。皆如此。如告子只知甘酸辛咸在饮食。而不知甘酸辛咸在口。故有义外之说。如释氏略知甘酸辛咸在口。而不知甘酸辛咸在物。故有绝物之心。其不可行均矣。理气先后说
朱子曰。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若论气禀。则有是气而后。理随而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朱子说止此。)愚按前段先言理也。后段先言气也。学者但知先言理而不知先言气。则浮泛忽略。有工夫疏脱之病矣。但知先言气而不知先言理。则糊涂昆仑。有本原昏昧之病矣。二病虽殊。其学之不成均也。如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一段。所以发明理先也。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一段。所以发明气先也。易曰。太极生两仪。即理先之原也。成之者性。即理后之分也。两说该备然后。总一太极各一太极。分合分明。潜心推究。久当自见。本原昏昧则必无主宰存养之地矣。工夫疏略则必无省察克治之事矣。学者不可不两讲也。癸亥至月十三日。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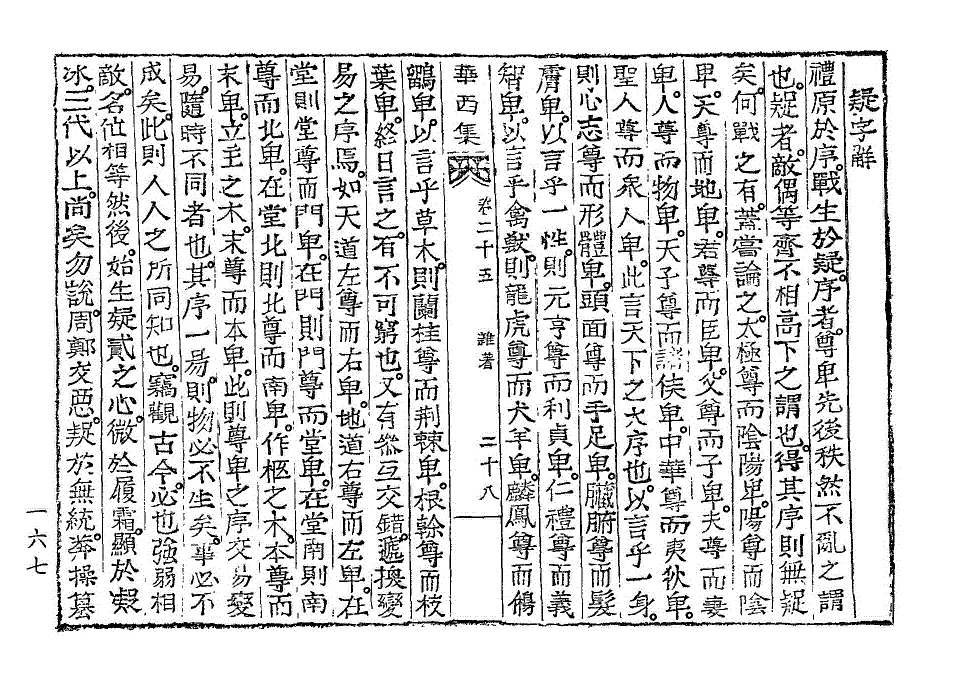 疑字解
疑字解礼原于序。战生于疑。序者。尊卑先后秩然不乱之谓也。疑者。敌偶等齐不相高下之谓也。得其序则无疑矣。何战之有。盖尝论之。太极尊而阴阳卑。阳尊而阴卑。天尊而地卑。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妻卑。人尊而物卑。天子尊而诸侯卑。中华尊而夷狄卑。圣人尊而众人卑。此言天下之大序也。以言乎一身。则心志尊而形体卑。头面尊而手足卑。脏腑尊而发肤卑。以言乎一性。则元亨尊而利贞卑。仁礼尊而义智卑。以言乎禽兽。则龙虎尊而犬羊卑。麟凤尊而鸺鹠卑。以言乎草木。则兰桂尊而荆棘卑。根干尊而枝叶卑。终日言之。有不可穷也。又有参互交错。递换变易之序焉。如天道左尊而右卑。地道右尊而左卑。在堂则堂尊而门卑。在门则门尊而堂卑。在堂南则南尊而北卑。在堂北则北尊而南卑。作柩之木。本尊而末卑。立主之木。末尊而本卑。此则尊卑之序交易变易。随时不同者也。其序一易。则物必不生矣。事必不成矣。此则人人之所同知也。窃观古今。必也强弱相敌。名位相等然后。始生疑贰之心。微于履霜。显于凝冰。三代以上。尚矣勿说。周郑交恶。疑于无统。莽操篡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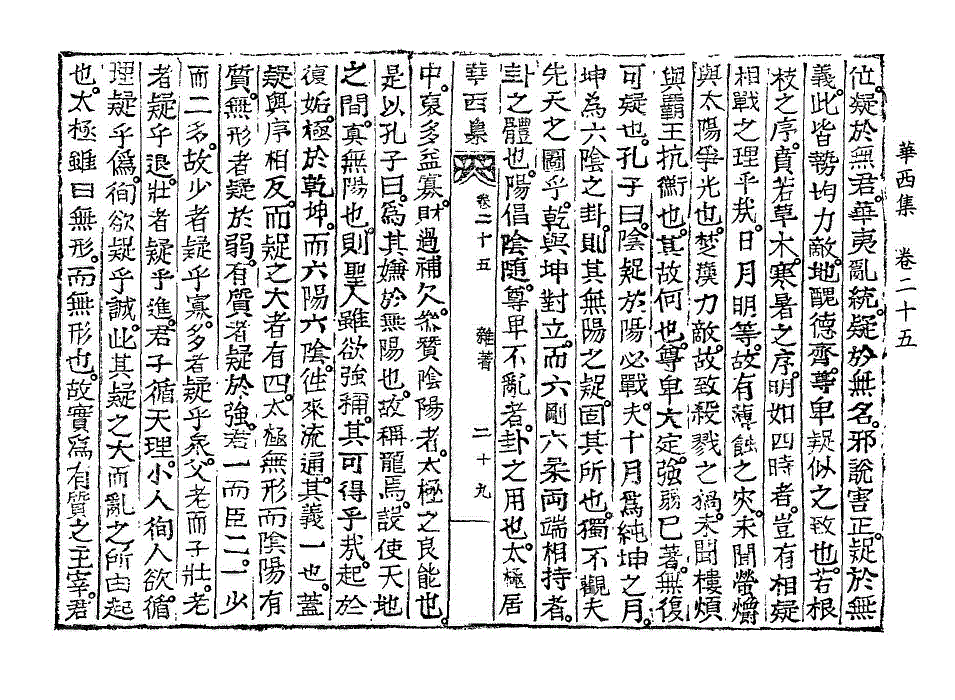 位。疑于无君。华夷乱统。疑于无名。邪说害正。疑于无义。此皆势均力敌。地丑德齐。尊卑疑似之致也。若根枝之序。贲若草木。寒暑之序。明如四时者。岂有相疑相战之理乎哉。日月明等。故有薄蚀之灾。未闻萤爝与太阳争光也。楚汉力敌。故致杀戮之祸。未闻楼烦与霸王抗衡也。其故何也。尊卑大定。强弱已著。无复可疑也。孔子曰。阴疑于阳必战。夫十月为纯坤之月。坤为六阴之卦。则其无阳之疑。固其所也。独不观夫先天之图乎。乾与坤对立。而六刚六柔两端相持者。卦之体也。阳倡阴随。尊卑不乱者。卦之用也。太极居中。裒多益寡。财过补欠。参赞阴阳者。太极之良能也。是以孔子曰。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设使天地之间。真无阳也。则圣人虽欲强称。其可得乎哉。起于复姤。极于乾坤。而六阳六阴。往来流通。其义一也。盖疑与序相反。而疑之大者有四。太极无形而阴阳有质。无形者疑于弱。有质者疑于强。君一而臣二。一少而二多。故少者疑乎寡。多者疑乎众。父老而子壮。老者疑乎退。壮者疑乎进。君子循天理。小人徇人欲。循理疑乎伪。徇欲疑乎诚。此其疑之大而乱之所由起也。太极虽曰无形。而无形也。故实为有质之主宰。君
位。疑于无君。华夷乱统。疑于无名。邪说害正。疑于无义。此皆势均力敌。地丑德齐。尊卑疑似之致也。若根枝之序。贲若草木。寒暑之序。明如四时者。岂有相疑相战之理乎哉。日月明等。故有薄蚀之灾。未闻萤爝与太阳争光也。楚汉力敌。故致杀戮之祸。未闻楼烦与霸王抗衡也。其故何也。尊卑大定。强弱已著。无复可疑也。孔子曰。阴疑于阳必战。夫十月为纯坤之月。坤为六阴之卦。则其无阳之疑。固其所也。独不观夫先天之图乎。乾与坤对立。而六刚六柔两端相持者。卦之体也。阳倡阴随。尊卑不乱者。卦之用也。太极居中。裒多益寡。财过补欠。参赞阴阳者。太极之良能也。是以孔子曰。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设使天地之间。真无阳也。则圣人虽欲强称。其可得乎哉。起于复姤。极于乾坤。而六阳六阴。往来流通。其义一也。盖疑与序相反。而疑之大者有四。太极无形而阴阳有质。无形者疑于弱。有质者疑于强。君一而臣二。一少而二多。故少者疑乎寡。多者疑乎众。父老而子壮。老者疑乎退。壮者疑乎进。君子循天理。小人徇人欲。循理疑乎伪。徇欲疑乎诚。此其疑之大而乱之所由起也。太极虽曰无形。而无形也。故实为有质之主宰。君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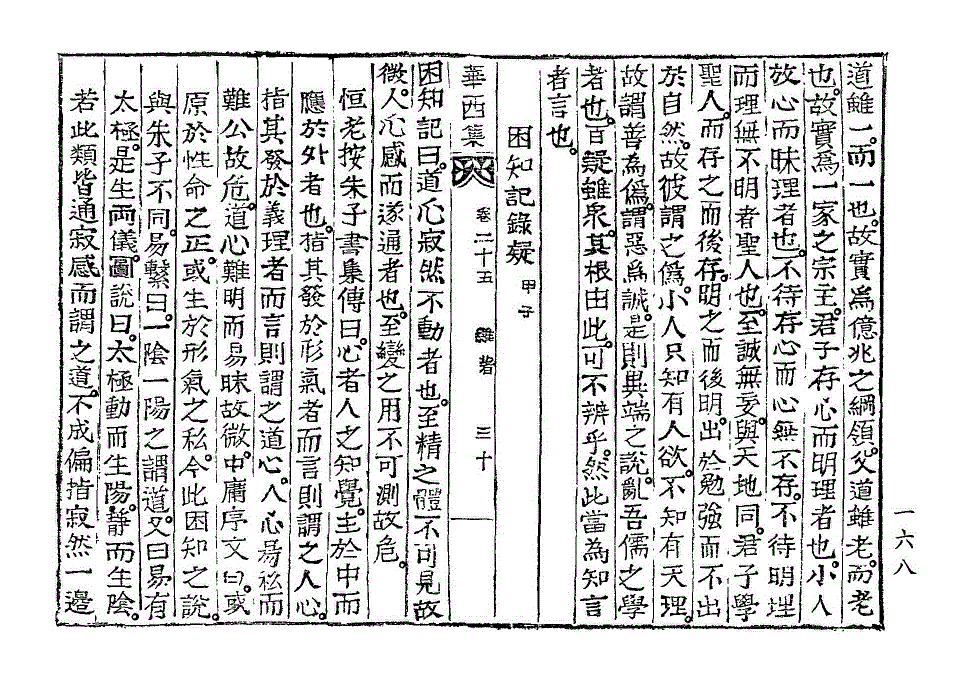 道虽一。而一也。故实为亿兆之纲领。父道虽老。而老也。故实为一家之宗主。君子存心而明理者也。小人放心而昧理者也。不待存心而心无不存。不待明理而理无不明者圣人也。至诚无妄。与天地同。君子学圣人。而存之而后存。明之而后明。出于勉强而不出于自然。故彼谓之伪。小人只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故谓善为伪。谓恶为诚。是则异端之说。乱吾儒之学者也。百疑虽众。其根由此。可不辨乎。然此当为知言者言也。
道虽一。而一也。故实为亿兆之纲领。父道虽老。而老也。故实为一家之宗主。君子存心而明理者也。小人放心而昧理者也。不待存心而心无不存。不待明理而理无不明者圣人也。至诚无妄。与天地同。君子学圣人。而存之而后存。明之而后明。出于勉强而不出于自然。故彼谓之伪。小人只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故谓善为伪。谓恶为诚。是则异端之说。乱吾儒之学者也。百疑虽众。其根由此。可不辨乎。然此当为知言者言也。困知记录疑(甲子)
困知记曰。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
恒老按朱子书集传曰。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中庸序文曰。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今此困知之说。与朱子不同。易系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若此类皆通寂感而谓之道。不成偏指寂然一边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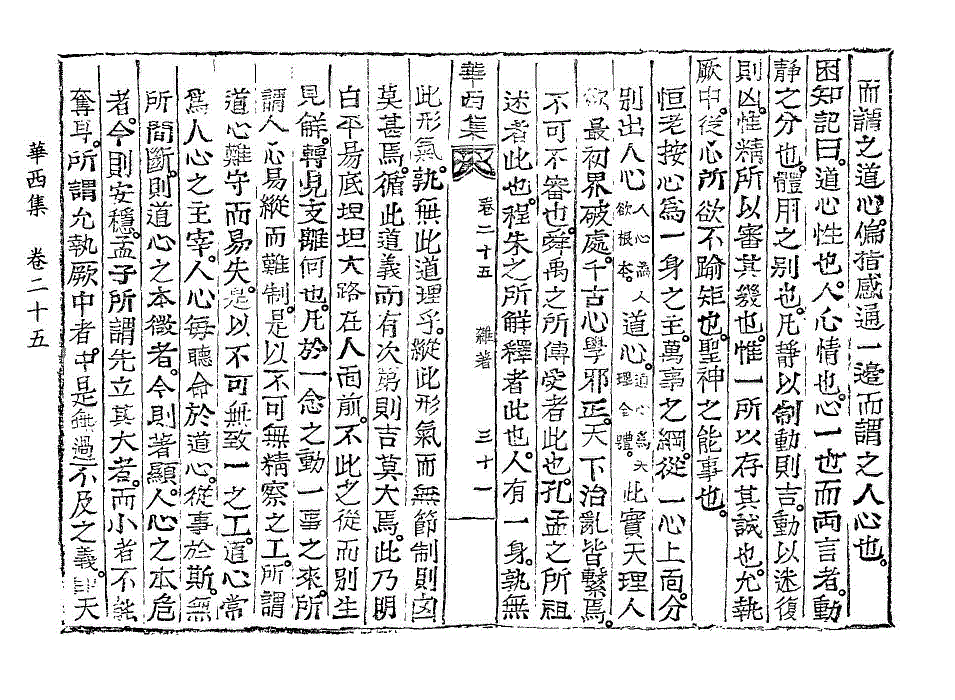 而谓之道心。偏指感通一边而谓之人心也。
而谓之道心。偏指感通一边而谓之人心也。困知记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者。动静之分也。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以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踰矩也。圣神之能事也。
恒老按心为一身之主。万事之纲。从一心上面。分别出人心(人心为人欲根本。)道心。(道心为天理全体。)此实天理人欲最初界破处。千古心学邪正。天下治乱皆系焉。不可不审也。舜禹之所传受者此也。孔孟之所祖述者此也。程朱之所解释者此也。人有一身。孰无此形气。孰无此道理乎。纵此形气而无节制则凶莫甚焉。循此道义而有次第则吉莫大焉。此乃明白平易底坦坦大路在人面前。不此之从而别生见解。转见支离何也。凡于一念之动一事之来。所谓人心易纵而难制。是以不可无精察之工。所谓道心难守而易失。是以不可无致一之工。道心常为人心之主宰。人心每听命于道心。从事于斯。无所间断。则道心之本微者。今则著显。人心之本危者。今则安稳。孟子所谓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耳。所谓允执厥中者。中是无过不及之义。即天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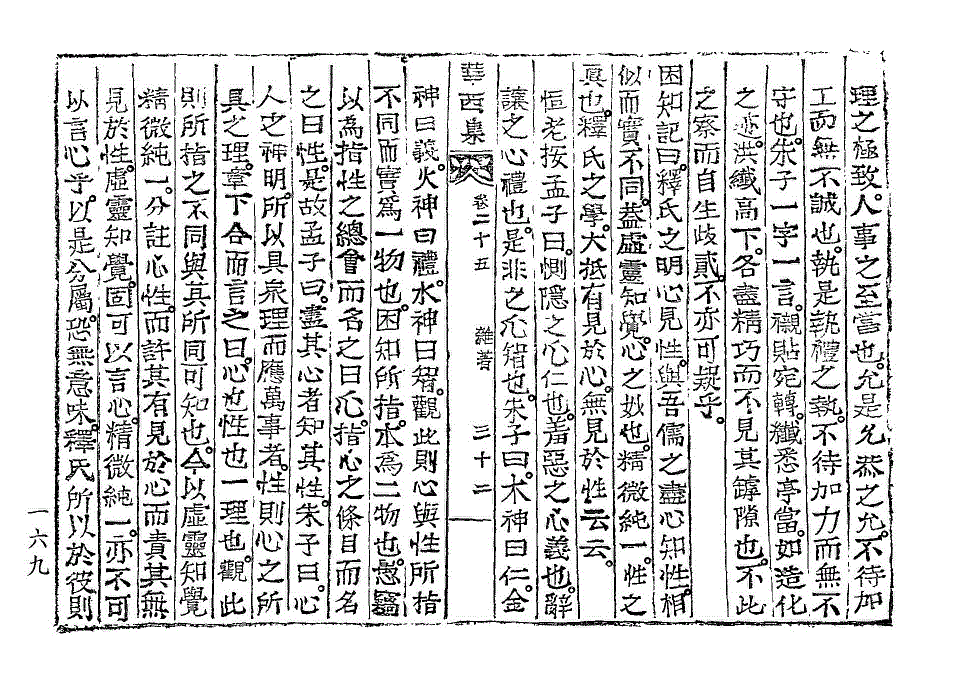 理之极致。人事之至当也。允是允恭之允。不待加工而无不诚也。执是执礼之执。不待加力而无不守也。朱子一字一言。衬贴宛转。纤悉亭当。如造化之迹。洪纤高下。各尽精巧而不见其罅隙也。不此之察而自生歧贰。不亦可疑乎。
理之极致。人事之至当也。允是允恭之允。不待加工而无不诚也。执是执礼之执。不待加力而无不守也。朱子一字一言。衬贴宛转。纤悉亭当。如造化之迹。洪纤高下。各尽精巧而不见其罅隙也。不此之察而自生歧贰。不亦可疑乎。困知记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云云。
恒老按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朱子曰。木神曰仁。金神曰义。火神曰礼。水神曰智。观此则心与性所指不同而实为一物也。困知所指。本为二物也。愚窃以为指性之总会而名之曰心。指心之条目而名之曰性。是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朱子曰。心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性则心之所具之理。章下合而言之曰。心也性也一理也。观此则所指之不同与其所同可知也。今以虚灵知觉精微纯一。分注心性。而许其有见于心而责其无见于性虚灵知觉。固可以言心。精微纯一。亦不可以言心乎。以是分属。恐无意味。释氏所以于彼则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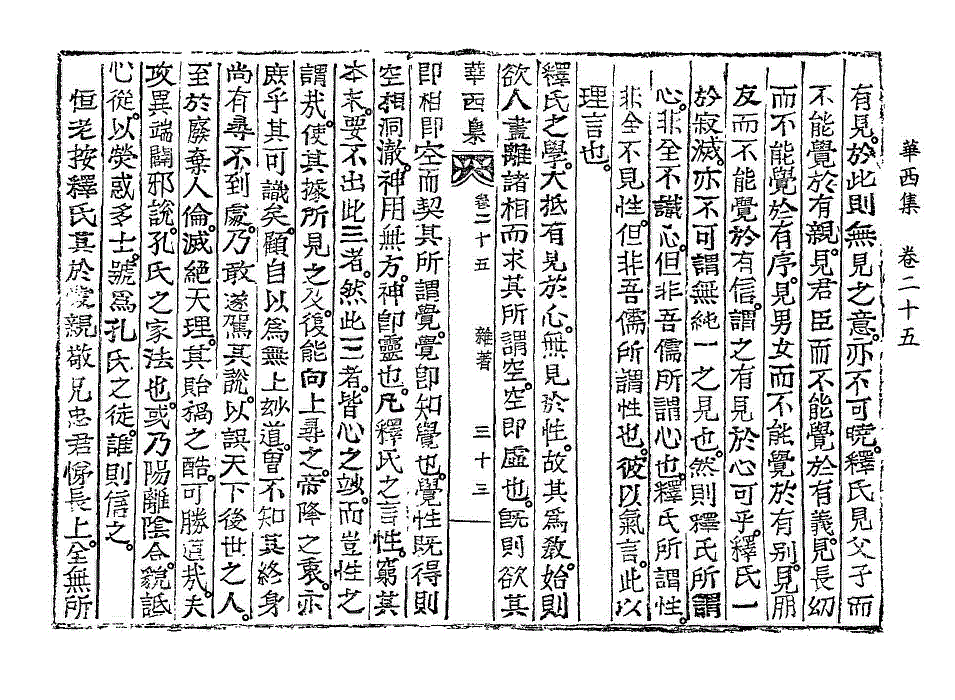 有见。于此则无见之意。亦不可晓。释氏见父子而不能觉于有亲。见君臣而不能觉于有义。见长幼而不能觉于有序。见男女而不能觉于有别。见朋友而不能觉于有信。谓之有见于心可乎。释氏一于寂灭。亦不可谓无纯一之见也。然则释氏所谓心。非全不识心。但非吾儒所谓心也。释氏所谓性。非全不见性。但非吾儒所谓性也。彼以气言。此以理言也。
有见。于此则无见之意。亦不可晓。释氏见父子而不能觉于有亲。见君臣而不能觉于有义。见长幼而不能觉于有序。见男女而不能觉于有别。见朋友而不能觉于有信。谓之有见于心可乎。释氏一于寂灭。亦不可谓无纯一之见也。然则释氏所谓心。非全不识心。但非吾儒所谓心也。释氏所谓性。非全不见性。但非吾儒所谓性也。彼以气言。此以理言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相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既则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谓觉。觉即知觉也。觉性既得则空相洞澈。神用无方。神即灵也。凡释氏之言性。穷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顾自以为无上妙道。曾不知其终身尚有寻不到处。乃敢遂驾其说。以误天下后世之人。至于废弃人伦。灭绝天理。其贻祸之酷。可胜道哉。夫攻异端辟邪说。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阳离阴合。貌诋心从。以荧惑多士。号为孔氏之徒。谁则信之。
恒老按释氏其于爱亲敬兄忠君悌长上。全无所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0L 页
 觉。则其所谓觉。与吾所谓觉。不翅相远。此可曰心之妙也哉。困知记乃曰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愚以为其本已差。而向上寻之。则愈见其相远。虚妄怪诞。岂可胜言哉。其有见于心。终不可晓。
觉。则其所谓觉。与吾所谓觉。不翅相远。此可曰心之妙也哉。困知记乃曰此三者。皆心之妙。而岂性之谓哉。使其据所见之及。复能向上寻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识矣。愚以为其本已差。而向上寻之。则愈见其相远。虚妄怪诞。岂可胜言哉。其有见于心。终不可晓。困知记曰。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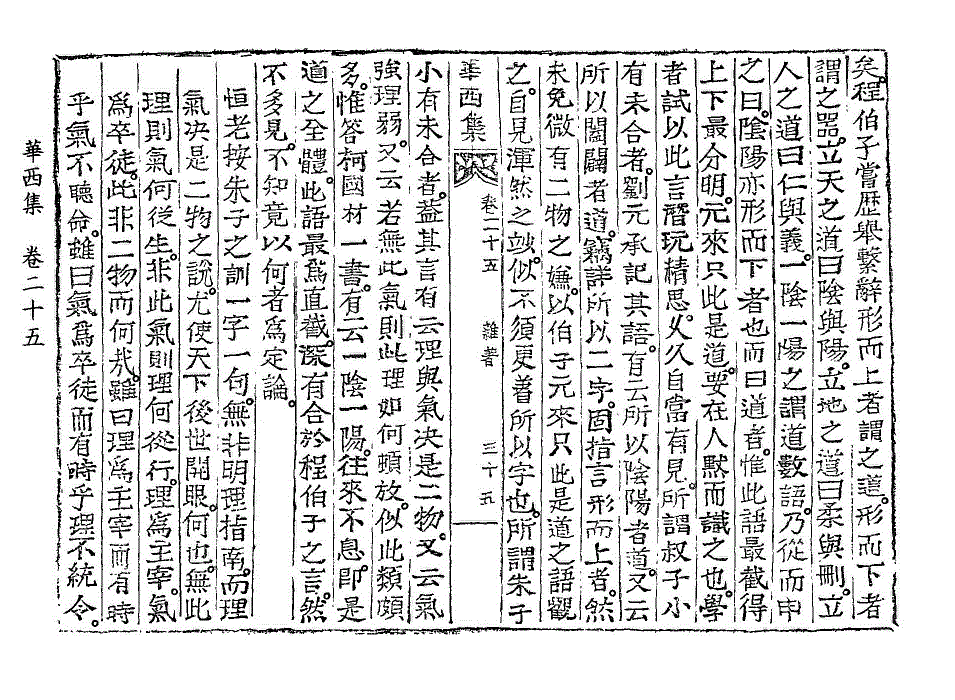 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最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久久自当有见。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
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最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久久自当有见。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恒老按朱子之训一字一句。无非明理指南。而理气决是二物之说。尤使天下后世开眼。何也。无此理则气何从生。非此气则理何从行。理为主宰。气为卒徒。此非二物而何哉。虽曰理为主宰而有时乎气不听命。虽曰气为卒徒而有时乎理不统令。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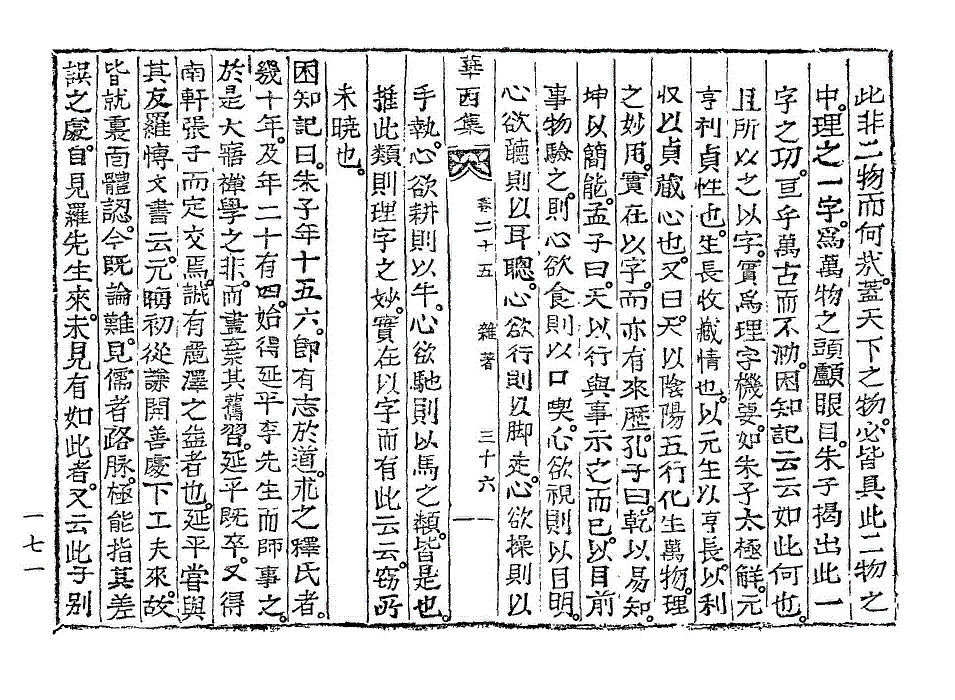 此非二物而何哉。盖天下之物。必皆具此二物之中。理之一字。为万物之头颅眼目。朱子揭出此一字之功。亘乎万古而不泐。困知记云云如此何也。且所以之以字。实为理字机要。如朱子太极解。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心也。又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理之妙用。实在以字。而亦有来历。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孟子曰。天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以目前事物验之。则心欲食则以口吃。心欲视则以目明。心欲听则以耳聪。心欲行则以脚走。心欲操则以手执。心欲耕则以牛。心欲驰则以马之类。皆是也。推此类则理字之妙。实在以字而有此云云。窃所未晓也。
此非二物而何哉。盖天下之物。必皆具此二物之中。理之一字。为万物之头颅眼目。朱子揭出此一字之功。亘乎万古而不泐。困知记云云如此何也。且所以之以字。实为理字机要。如朱子太极解。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心也。又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理之妙用。实在以字。而亦有来历。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孟子曰。天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以目前事物验之。则心欲食则以口吃。心欲视则以目明。心欲听则以耳聪。心欲行则以脚走。心欲操则以手执。心欲耕则以牛。心欲驰则以马之类。皆是也。推此类则理字之妙。实在以字而有此云云。窃所未晓也。困知记曰。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于道。求之释氏者。几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师事之。于是大寤禅学之非。而尽弃其旧习。延平既卒。又得南轩张子而定交焉。诚有丽泽之益者也。延平尝与其友罗博文书云。元晦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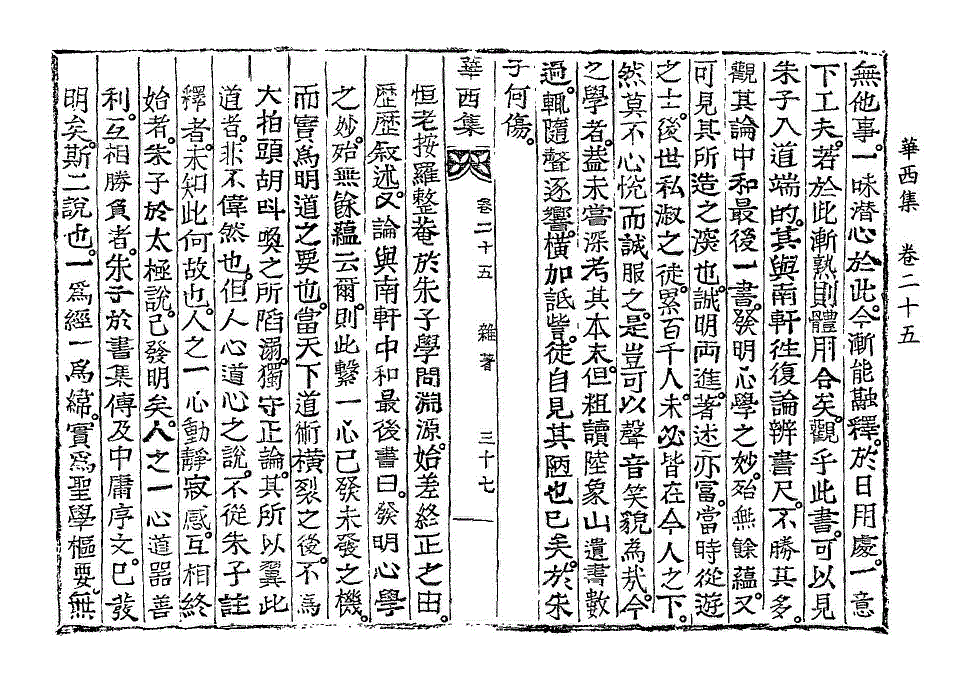 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观乎此书。可以见朱子入道端的。其与南轩往复论辨书尺。不胜其多。观其论中和最后一书。发明心学之妙。殆无馀蕴。又可见其所造之深也。诚明两进。著述亦富。当时从游之士。后世私淑之徒。累百千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悦而诚服之。是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今之学者。盖未尝深考其本末。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辄随声逐响。横加诋訾。徒自见其陋也已矣。于朱子何伤。
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观乎此书。可以见朱子入道端的。其与南轩往复论辨书尺。不胜其多。观其论中和最后一书。发明心学之妙。殆无馀蕴。又可见其所造之深也。诚明两进。著述亦富。当时从游之士。后世私淑之徒。累百千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悦而诚服之。是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今之学者。盖未尝深考其本末。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辄随声逐响。横加诋訾。徒自见其陋也已矣。于朱子何伤。恒老按罗整庵于朱子学问渊源。始差终正之由。历历叙述。又论与南轩中和最后书曰。发明心学之妙。殆无馀蕴云尔。则此系一心已发未发之机。而实为明道之要也。当天下道术横裂之后。不为大拍头胡叫唤之所陷溺。独守正论。其所以翼此道者。非不伟然也。但人心道心之说。不从朱子注释者。未知此何故也。人之一心动静寂感。互相终始者。朱子于太极说。已发明矣。人之一心道器善利。互相胜负者。朱子于书集传及中庸序文。已发明矣。斯二说也。一为经一为纬。实为圣学枢要。无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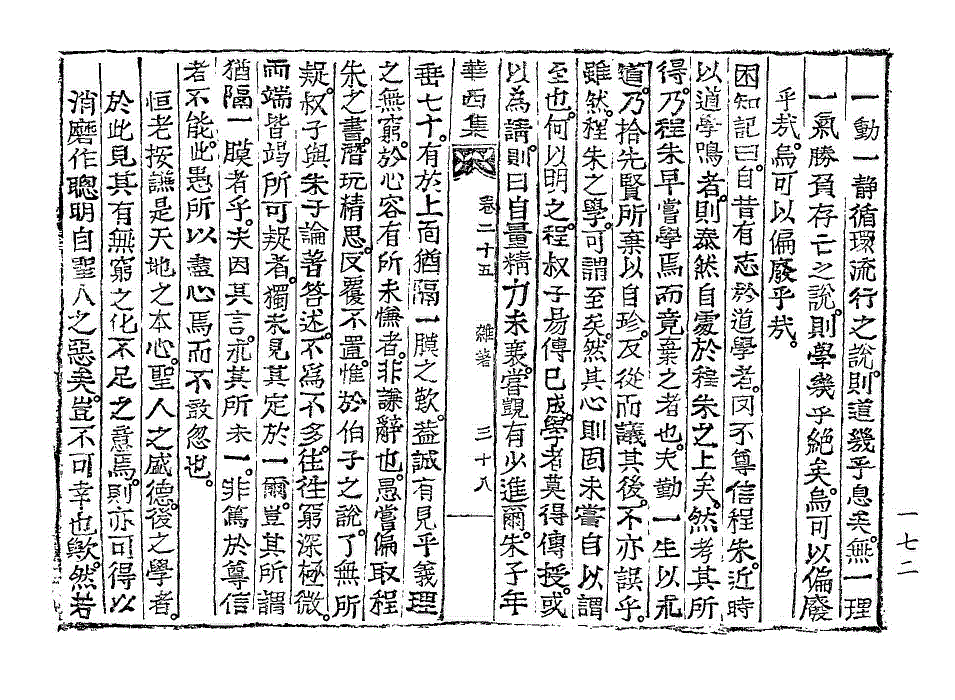 一动一静循环流行之说。则道几乎息矣。无一理一气胜负存亡之说。则学几乎绝矣。乌可以偏废乎哉。乌可以偏废乎哉。
一动一静循环流行之说。则道几乎息矣。无一理一气胜负存亡之说。则学几乎绝矣。乌可以偏废乎哉。乌可以偏废乎哉。困知记曰。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鸣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尝学焉而竟弃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贤所弃以自珍。反从而议其后。不亦误乎。虽然。程朱之学。可谓至矣。然其心则固未尝自以谓至也。何以明之。程叔子易传已成。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则曰自量精力未衰。尝觊有少进尔。朱子年垂七十。有于上面犹隔一膜之叹。盖诚有见乎义理之无穷。于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谦辞也。愚尝偏取程朱之书。潜玩精思。反覆不置。惟于伯子之说。了无所疑。叔子与朱子论著答述。不为不多。往往穷深极微。两端皆竭所可疑者。独未见其定于一尔。岂其所谓犹隔一膜者乎。夫因其言。求其所未一。非笃于尊信者不能。此愚所以尽心焉而不敢忽也。
恒老按谦是天地之本心。圣人之盛德。后之学者。于此见其有无穷之化不足之意焉。则亦可得以消磨作聪明自圣人之恶矣。岂不可幸也欤。然若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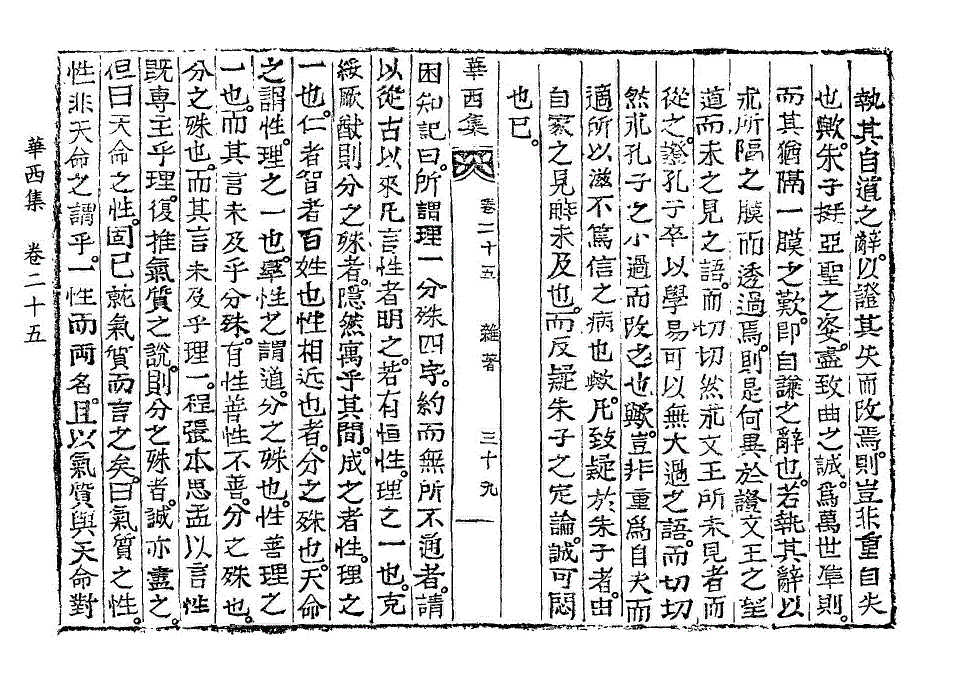 执其自道之辞。以證其失而改焉。则岂非重自失也欤。朱子挺亚圣之姿。尽致曲之诚。为万世准则。而其犹隔一膜之叹。即自谦之辞也。若执其辞以求所隔之膜而透过焉。则是何异于證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见之语。而切切然求文王所未见者而从之。證孔子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之语。而切切然求孔子之小过而改之也欤。岂非重为自夫而适所以滋不笃信之病也欤。凡致疑于朱子者。由自家之见解未及也。而反疑朱子之定论。诚可闷也已。
执其自道之辞。以證其失而改焉。则岂非重自失也欤。朱子挺亚圣之姿。尽致曲之诚。为万世准则。而其犹隔一膜之叹。即自谦之辞也。若执其辞以求所隔之膜而透过焉。则是何异于證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见之语。而切切然求文王所未见者而从之。證孔子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之语。而切切然求孔子之小过而改之也欤。岂非重为自夫而适所以滋不笃信之病也欤。凡致疑于朱子者。由自家之见解未及也。而反疑朱子之定论。诚可闷也已。困知记曰。所谓理一分殊四字。约而无所不通者。请以从古以来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绥厥猷则分之殊者。隐然寓乎其间。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智者百姓也性相近也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谓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谓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性不善。分之殊也。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张本思孟以言性既专主乎理。复推气质之说。则分之殊者。诚亦尽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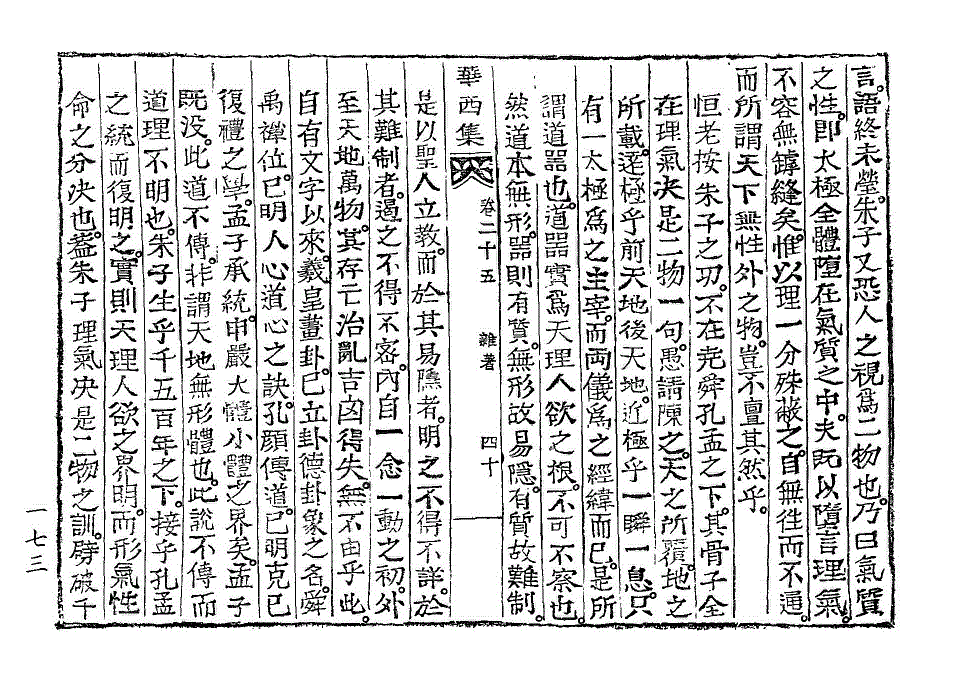 言。语终未莹。朱子又恐人之视为二物也。乃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而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岂不亶其然乎。
言。语终未莹。朱子又恐人之视为二物也。乃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而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岂不亶其然乎。恒老按朱子之功。不在尧舜孔孟之下。其骨子全在理气决是二物一句。愚请陈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远极乎前天地后天地。近极乎一瞬一息。只有一太极为之主宰。而两仪为之经纬而已。是所谓道器也。道器实为天理人欲之根。不可不察也。然道本无形。器则有质。无形故易隐。有质故难制。是以圣人立教。而于其易隐者。明之不得不详。于其难制者。遏之不得不密。内自一念一动之初。外至天地万物。其存亡治乱吉凶得失。无不由乎此。自有文字以来。羲皇画卦。已立卦德卦象之名。舜禹禅位。已明人心道心之诀。孔颜传道。已明克己复礼之学。孟子承统。申严大体小体之界矣。孟子既没。此道不传。非谓天地无形体也。此说不传而道理不明也。朱子生乎千五百年之下。接乎孔孟之统而复明之。实则天理人欲之界明。而形气性命之分决也。盖朱子理气决是二物之训。劈破千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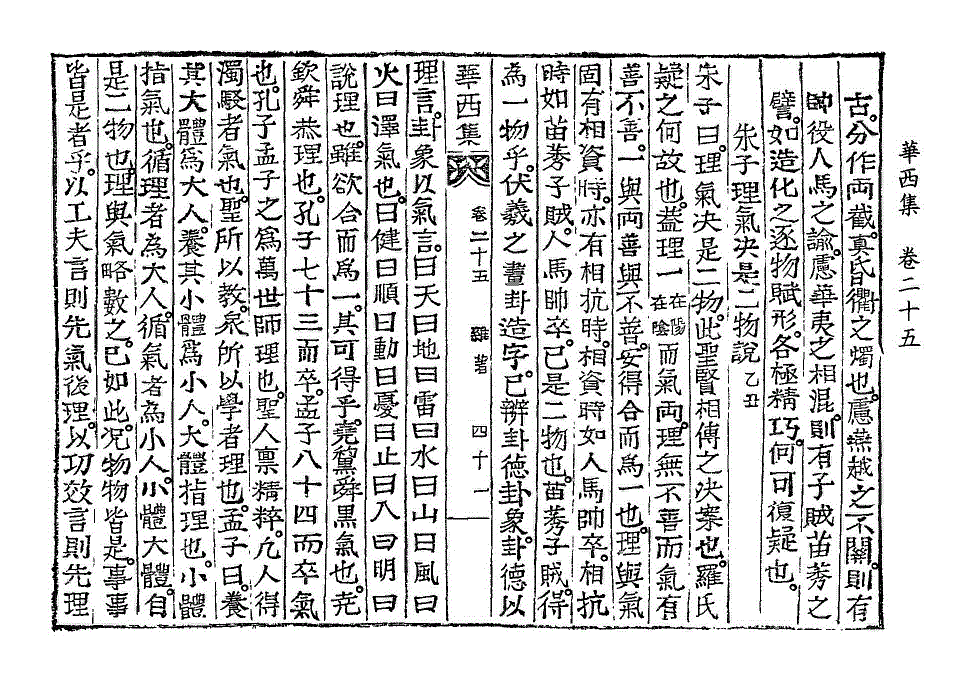 古。分作两截。真昏衢之烛也。虑燕越之不关。则有帅役人马之谕。虑华夷之相混。则有子贼苗莠之譬。如造化之逐物赋形。各极精巧。何可复疑也。
古。分作两截。真昏衢之烛也。虑燕越之不关。则有帅役人马之谕。虑华夷之相混。则有子贼苗莠之譬。如造化之逐物赋形。各极精巧。何可复疑也。朱子理气决是二物说(乙丑)
朱子曰。理气决是二物。此圣贤相传之决案也。罗氏疑之何故也。盖理一(在阳在阴)而气两。理无不善而气有善不善。一与两善与不善。安得合而为一也。理与气固有相资时。亦有相抗时。相资时如人马帅卒。相抗时如苗莠子贼。人马帅卒。已是二物也。苗莠子贼。得为一物乎。伏羲之画卦造字。已辨卦德卦象。卦德以理言。卦象以气言。曰天曰地曰雷曰水曰山曰风曰火曰泽气也。曰健曰顺曰动曰忧曰止曰入曰明曰说理也。虽欲合而为一。其可得乎。尧黧舜黑气也。尧钦舜恭理也。孔子七十三而卒。孟子八十四而卒气也。孔子孟子之为万世师理也。圣人禀精粹。凡人得浊驳者气也。圣所以教。众所以学者理也。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大体指理也。小体指气也。循理者为大人。循气者为小人。小体大体。自是二物也。理与气略数之。已如此。况物物皆是。事事皆是者乎。以工夫言则先气后理。以功效言则先理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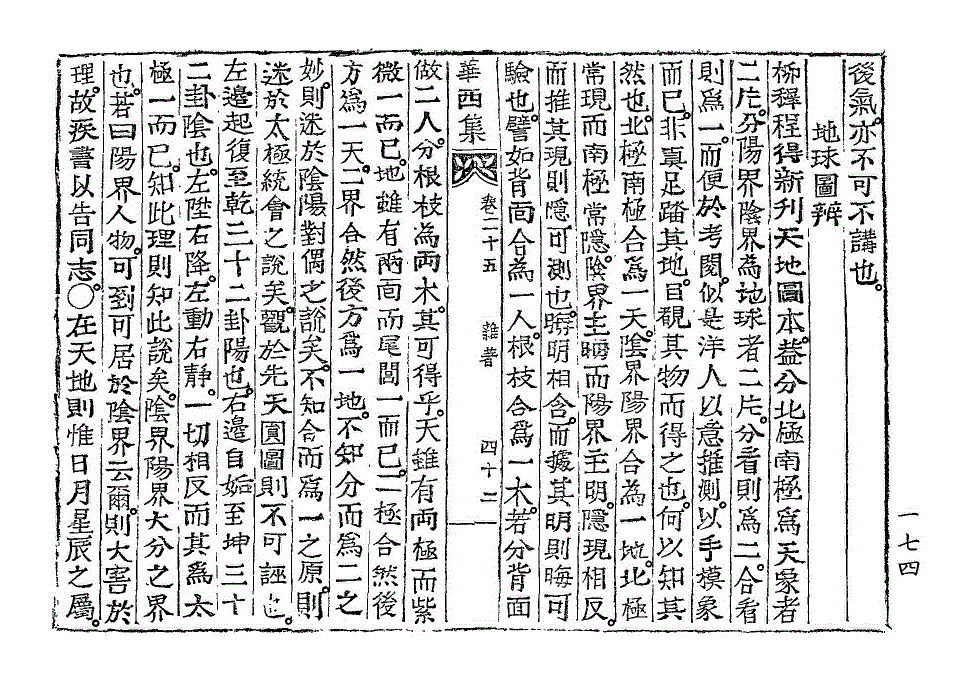 后气。亦不可不讲也。
后气。亦不可不讲也。地球图辨
柳𥠧程得新刊天地图本。盖分北极南极为天象者二片。分阳界阴界为地球者二片。分看则为二。合看则为一。而便于考阅。似是洋人以意推测。以手模象而已。非真足踏其地。目睹其物而得之也。何以知其然也。北极南极合为一天。阴界阳界合为一地。北极常现而南极常隐。阴界主晦而阳界主明。隐现相反。而推其现则隐可测也。晦明相含。而据其明则晦可验也。譬如背面合为一人。根枝合为一木。若分背面做二人。分根枝为两木。其可得乎。天虽有两极而紫微一而已。地虽有两面而尾闾一而已。二极合然后方为一天。二界合然后方为一地。不知分而为二之妙。则迷于阴阳对偶之说矣。不知合而为一之原。则迷于太极统会之说矣。观于先天圆图则不可诬也。左边起复至乾三十二卦阳也。右边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阴也。左升右降。左动右静。一切相反而其为太极一而已。知此理则知此说矣。阴界阳界大分之界也。若曰阳界人物。可到可居于阴界云尔。则大害于理。故疾书以告同志。○在天地则惟日月星辰之属。
华西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第 175H 页
 可以流行贯通乎阴阳两界。而血气死生之物。则决不能打过二界矣。在人则惟心志道理之属。可以淹贯包括乎阴阳两面。而身体形气之属。决不能打过两界矣。其故何也。日月运而人物滞故也。心志通而形气局故也。
可以流行贯通乎阴阳两界。而血气死生之物。则决不能打过二界矣。在人则惟心志道理之属。可以淹贯包括乎阴阳两面。而身体形气之属。决不能打过两界矣。其故何也。日月运而人物滞故也。心志通而形气局故也。太极图主静说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而先阳后阴。此则名位尊卑之序也。自圣人定之以下。先阴而后阳。此则工夫积累之序也。有基址根盘然后。施堂室门庭之功。有田地水土然后。积城郭耕耘之劳。此主静二字。为圣人教后学之最初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