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x 页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月城金正喜元春著)
[杂识]
[杂识]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5H 页
 杂识
杂识日躔黄道。一周历春夏秋冬。四时代序而成岁。一岁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是为岁实也。月离白道。一周历朔弦望晦。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古圣人因节气过宫。民不易晓。姑从合朔一周为一月。合朔十二周为一年。良以生明生魄。举头易见。取其便于授时。非为合朔十二周为即岁实也。岁实自为岁实。合朔自为合朔。在天各自运行。本非一轨。今既借合朔。以纪岁实。故岁实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气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有奇。较岁实少十一日弱。朔虚者此十一日弱也。二年则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将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闰。盖岁实满三周。则已历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而为闰也。
蔡注既云日行之数月行之数。而又云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此三百六十之常数。日月行度之外。又是何数也。是混囵无别。不可强解者一也。又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与天会而多五日。与日会少五日故一岁闰率则十日云云。其多五日者。可以入算。少五日者。又何以入算而成十日之数耶。是又混囵无别。不可强解者二也。
二十八宿之星。始见于周礼冯相氏。而其目不详。尔疋释天。星有十七宿。无女危胃觜参井鬼星张翼轸。月令廑二十六星。盖以建弧而无箕昴鬼张。史记历书。始详备二十八星之号。然有建罚狼弧。无斗觜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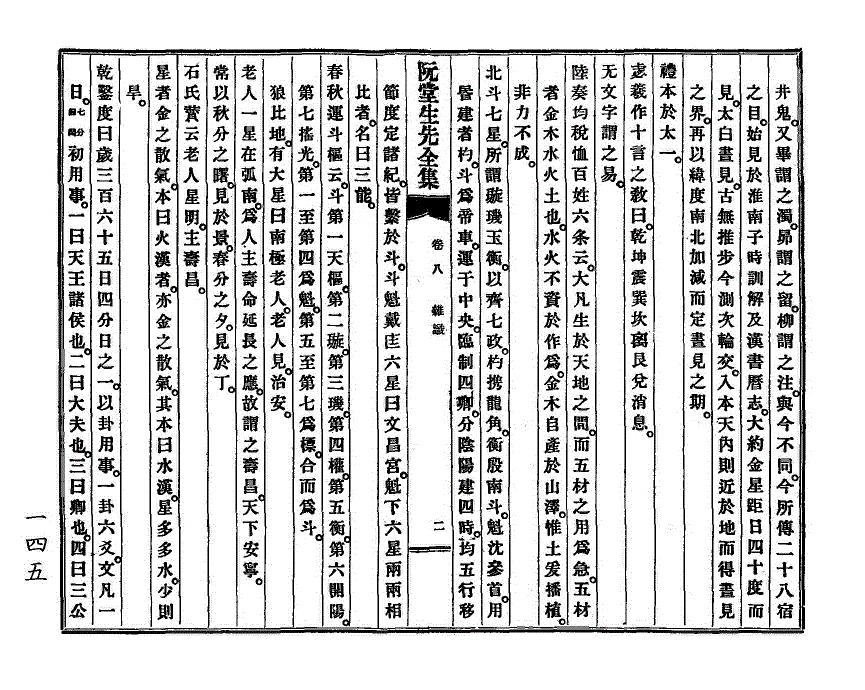 井鬼。又毕谓之浊。昴谓之留。柳谓之注。与今不同。今所传二十八宿之目。始见于淮南子时训解及汉书历志。大约金星距日四十度而见。太白昼见。古无推步今测次轮交。入本天内则近于地而得昼见之界。再以纬度南北加减而定昼见之期。
井鬼。又毕谓之浊。昴谓之留。柳谓之注。与今不同。今所传二十八宿之目。始见于淮南子时训解及汉书历志。大约金星距日四十度而见。太白昼见。古无推步今测次轮交。入本天内则近于地而得昼见之界。再以纬度南北加减而定昼见之期。礼本于太一。
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
无文字谓之易。
陆奏均税恤百姓六条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而五材之用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资于作为。金木自产于山泽。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沈参首。用昏建者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卿。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
春秋运斗枢云。斗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
老人一星在弧南。为人主寿命延长之应。故谓之寿昌。天下安宁。
常以秋分之曙。见于景。春分之夕。见于丁。
石氏赞云老人星明。主寿昌。
星者金之散气。本曰火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
乾凿度曰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文凡一日。(七分归闰)初用事。一曰天王诸侯也。二曰大夫也。三曰卿也。四曰三公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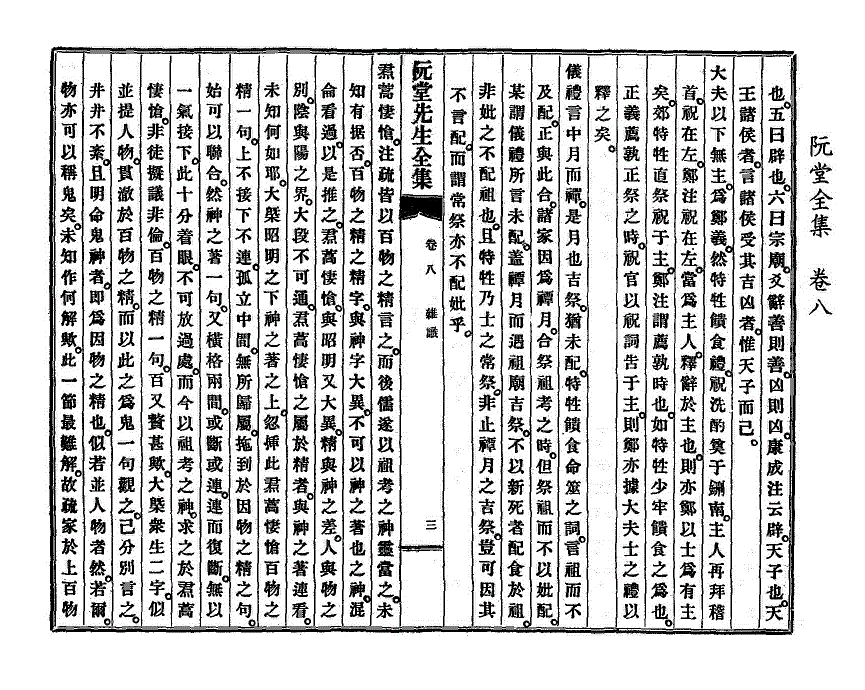 也。五曰辟也。六曰宗庙。爻辞善则善。凶则凶。康成注云辟。天子也。天王诸侯者。言诸侯受其吉凶者。惟天子而已。
也。五曰辟也。六曰宗庙。爻辞善则善。凶则凶。康成注云辟。天子也。天王诸侯者。言诸侯受其吉凶者。惟天子而已。大夫以下无主。为郑义。然特牲馈食礼。祝洗酌奠于铏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郑注祝在左。当为主人。释辞于主也。则亦郑以士为有主矣。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郑注谓荐孰时也。如特牲少牢馈食之为也。正义荐孰正祭之时。祝官以祝词告于主。则郑亦据大夫士之礼以释之矣。
仪礼言中月而禅。是月也吉祭。犹未配。特牲馈食命筮之词。言祖而不及配。正与此合。诸家因为禫月。合祭祖考之时。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谓仪礼所言未配。盖禫月而遇祖庙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于祖。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岂可因其不言配。而谓常祭亦不配妣乎。
焄蒿悽怆。注疏皆以百物之精言之。而后儒遂以祖考之神灵当之。未知有据否。百物之精之精字。与神字大异。不可以神之著也之神。混仑看过。以是推之。焄蒿悽怆。与昭明又大异。精与神之差。人与物之别。阴与阳之界。大段不可通。焄蒿悽怆之属于精者。与神之著连看。未知何如耶。大槩昭明之下神之著之上。忽插此焄蒿悽怆百物之精一句。上不接下不连。孤立中间。无所归属。拖到于因物之精之句。始可以联合。然神之著一句。又横格两间。或断或连。连而复断。无以一气接下。此十分着眼。不可放过处。而今以祖考之神。求之于焄蒿悽怆。非徒拟议非伦。百物之精一句。百又赘甚欤。大槩众生二字。似并提人物。贯澈于百物之精。而以此之为鬼一句观之。已分别言之。井井不紊。且明命鬼神者。即为因物之精也。似若并人物者然。若尔。物亦可以称鬼矣。未知作何解欤。此一节最难解。故疏家于上百物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6L 页
 之精。分别言之。于下因物之精。混并人物。无所分别。自昔之难读如此矣。
之精。分别言之。于下因物之精。混并人物。无所分别。自昔之难读如此矣。大学明明德。郑注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今汲古阁本。显字讹在字。明明者显明之义。诗鲁颂在公明明。笺亦引大学为證。孔疏以身有明德为说。非郑义也。
孟子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此谓仁犹人之所以为心。义犹人之所以为路。非为即心即仁也。若云此仁即真是心。断不可云此义即真是路也。总之。圣贤之仁。必偶于人而始可见。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见安怀。若心无所着。便可为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毕仁之事有是道乎。
孟子仁也者人也。中庸仁者人也。语意不同。仁也者人也者。即能行仁恩者人也。中庸人也者。郑读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即人意相存问之义也。
平实精详。一部经解之要。平则不骛高远而切问近思。实则不落空虚而好古求是。非明辨则不能精。非博学则不能详。即如荀子者。学出孔门。受授诸经。尤传诗礼。而韩昌黎斥为择而不精。语而不详。盖昌黎但知文。不知经者也。易奇诗葩。不过择其词语为文之资而已。非余所谓精详也。不独昌黎为然。陆元朗知等韵。不知古韵。信伪古文尚书。以舜典廿八字。升为经文。李斯以后一罪人也。孔冲远袭皇甫熊刘之书。古今文不分。南北学不别。自孔疏出而先秦两汉古义亡。先秦两汉古义既亡。七十子微言大义益乖。欧阳夏侯齐鲁韩古书。单词只义。是在考古者甄录之。即如北史及通典所载古义。不可补贾公彦之弇陋哉。
姜白石尧章云世传仲尼表季札墓云云。以白石之精博于金石。不援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7H 页
 引古书。而只云世传。则古书之不见。可以溯知。又欧公云考仲尼历聘。不闻至吴。又其字特大。非古也。且按旧碑字大尺馀。墓阙题字。始于东汉有之。春秋以上。未闻有铭镌于礼碑桓楹者。此为后人依托确甚。不见于古书宜矣。唐张从申跋云玄宗尝命殷仲容摹榻。大历中。润州刺史萧定作季子庙。重刻此碑。传至今。其最古可徵者。为唐人文字耳。
引古书。而只云世传。则古书之不见。可以溯知。又欧公云考仲尼历聘。不闻至吴。又其字特大。非古也。且按旧碑字大尺馀。墓阙题字。始于东汉有之。春秋以上。未闻有铭镌于礼碑桓楹者。此为后人依托确甚。不见于古书宜矣。唐张从申跋云玄宗尝命殷仲容摹榻。大历中。润州刺史萧定作季子庙。重刻此碑。传至今。其最古可徵者。为唐人文字耳。日本文字之起。自百济王仁始。而其国书。其国所称黄备氏所制也。其时不通中国。凡系中国书籍。皆资于我。今足利学所存古经。即唐以前旧迹也。尝得见尚书翻雕者。与齐梁二金石字体相同。又似新罗真兴王碑字。是必于王仁时所得去者。至今千有馀年。藏弃无恙。此寔天下之所无也。且如皇侃论语义疏。萧吉五行大义等书。皆中国之已佚。尚存于彼。何其异也。晁监奝然。今不可考。三西京东都之间。其所为文。弇陋僻谬。随其语言。直行文势。无俯仰转折上下吐纳之义。如武林传。至无以句读者也。而百馀年来。藤树物部之学大盛。诗文专尚沧溟。稍变俗体。然旧染已痼。猝难革面矣。今见东都人筱四本廉文字三篇。一洗弇陋僻谬之习。词采焕发。又不用沧溟文格。虽中国作手。无以加之。噫。长崎之舶。日与中国呼吸相注。丝铜贸迁。尚属第二。天下书籍。无不海输山运。
古今诗法。至陶靖节。为一结穴。唐之王右丞,杜工部。各为一结穴。王如天衣无缝。如天女散花。曼多曼少。非世间凡卉所可比拟。杜如土石瓦塼。自地筑起。五凤楼材。称剂其轻重以成之。一是神理。一是实境。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似若各一门户。然禹稷与颜。其揆一也。无用分别同异。能透得此关然后可以言诗。如李义山,杜樊川。皆工部之嫡派。白香山又为一结穴。不愧其广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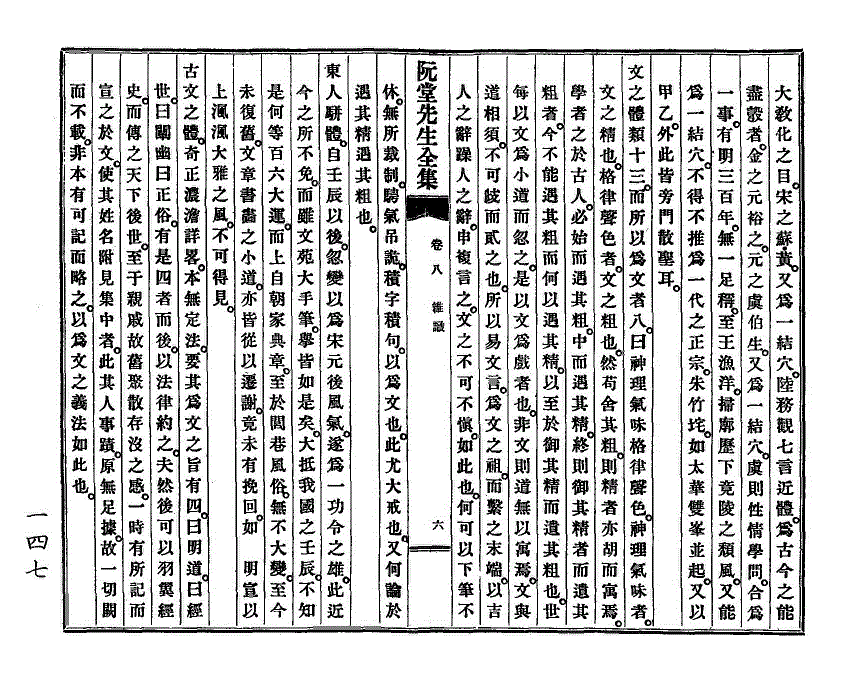 大教化之目。宋之苏,黄。又为一结穴。陆务观七言近体。为古今之能尽彀者。金之元裕之。元之虞伯生。又为一结穴。虞则性情学问。合为一事。有明三百年。无一足称。至王渔洋。扫廓历下竟陵之颓风。又能为一结穴。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朱竹垞。如太华双峰并起。又以甲乙。外此皆旁门散圣耳。
大教化之目。宋之苏,黄。又为一结穴。陆务观七言近体。为古今之能尽彀者。金之元裕之。元之虞伯生。又为一结穴。虞则性情学问。合为一事。有明三百年。无一足称。至王渔洋。扫廓历下竟陵之颓风。又能为一结穴。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朱竹垞。如太华双峰并起。又以甲乙。外此皆旁门散圣耳。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而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今不能遇其粗而何以遇其精。以至于御其精而遗其粗也。世每以文为小道而忽之。是以文为戏者也。非文则道无以寓焉。文与道相须。不可歧而贰之也。所以易文言。为文之祖。而系之末端。以吉人之辞躁人之辞。申复言之。文之不可不慎。如此也。何可以下笔不休。无所裁制。骋气吊诡。积字积句。以为文也。此尤大戒也。又何论于遇其精遇其粗也。
东人骈体。自壬辰以后。忽变以为宋元后风气。遂为一功令之雄。此近今之所不免。而虽文苑大手笔。举皆如是矣。大抵我国之壬辰。不知是何等百六大运。而上自朝家典章。至于闾巷风俗。无不大变。至今未复旧。文章书画之小道。亦皆从以迁谢。竟未有挽回。如 明宣以上沨沨大雅之风。不可得见。
古文之体。奇正浓澹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至于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一时有所记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见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无足据。故一切阙而不载。非本有可记而略之。以为文之义法如此也。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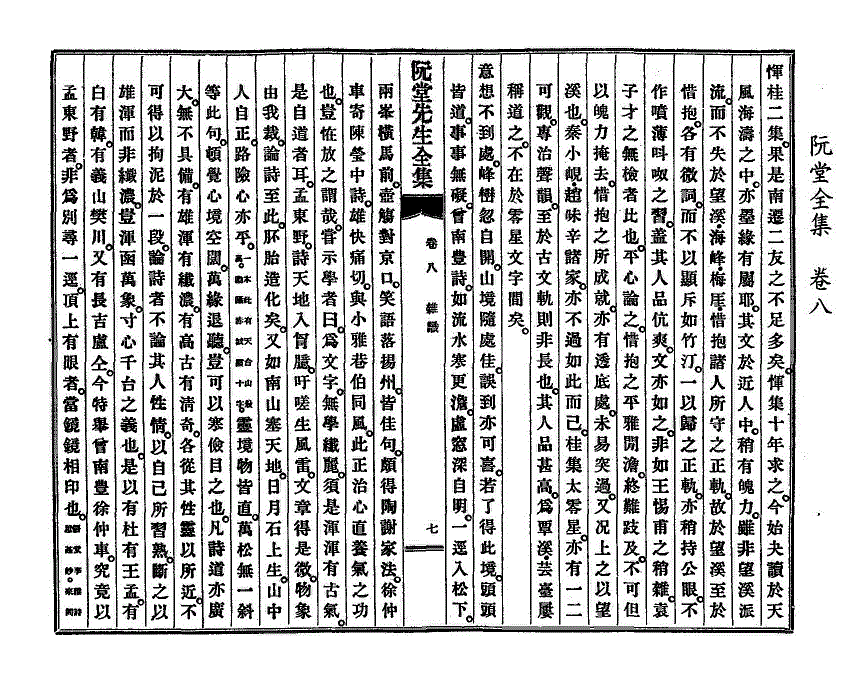 恽桂二集。果是南迁二友之不足多矣。恽集十年求之。今始夬读于天风海涛之中。亦墨缘有属耶。其文于近人中。稍有魄力。虽非望溪派流。而不失于望溪,海峰,梅厓,惜抱诸人所守之正轨。故于望溪至于惜抱。各有微词。而不以显斥如竹汀。一以归之正轨。亦稍持公眼。不作喷薄叫呶之习。盖其人品伉爽。文亦如之。非如王惕甫之稍杂。袁子才之无检者比也。平心论之。惜抱之平雅閒澹。终难跂及。不可但以魄力掩去。惜抱之所成就。亦有透底处。未易突过。又况上之以望溪也。秦小岘,赵昧辛诸家。亦不过如此而已。桂集太零星。亦有一二可观。专治声韵。至于古文轨则非长也。其人品甚高。为覃溪,芸台屡称道之。不在于零星文字间矣。
恽桂二集。果是南迁二友之不足多矣。恽集十年求之。今始夬读于天风海涛之中。亦墨缘有属耶。其文于近人中。稍有魄力。虽非望溪派流。而不失于望溪,海峰,梅厓,惜抱诸人所守之正轨。故于望溪至于惜抱。各有微词。而不以显斥如竹汀。一以归之正轨。亦稍持公眼。不作喷薄叫呶之习。盖其人品伉爽。文亦如之。非如王惕甫之稍杂。袁子才之无检者比也。平心论之。惜抱之平雅閒澹。终难跂及。不可但以魄力掩去。惜抱之所成就。亦有透底处。未易突过。又况上之以望溪也。秦小岘,赵昧辛诸家。亦不过如此而已。桂集太零星。亦有一二可观。专治声韵。至于古文轨则非长也。其人品甚高。为覃溪,芸台屡称道之。不在于零星文字间矣。意想不到处。峰峦忽自开。山境随处佳。误到亦可喜。若了得此境。头头皆道。事事无碍。曾南礼诗。如流水寒更澹。虚窗深自明。一径入松下。两峰横马前。壶觞对京口。笑语落扬州。皆佳句。颇得陶谢家法。徐仲车寄陈莹中诗。雄快痛切。与小雅巷伯同风。此正治心直养气之功也。岂怪放之谓哉。尝示学者曰。为文字。无学纤丽。须是浑浑有古气。是自道者耳。孟东野。诗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是微。物象由我裁。论诗至此。胚胎造化矣。又如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一本此有天台山最高。动蹑赤城霞十字。)灵境物皆直。万松无一斜等此句。顿觉心境空阔。万缘退听。岂可以寒俭目之也。凡诗道亦广大。无不具备。有雄浑有纤浓。有高古有清奇。各从其性灵以所近。不可得以拘泥于一段。论诗者不论其人性情。以自己所习熟。断之以雄浑而非纤浓。岂浑函万象。寸心千台之义也。是以有杜有王孟。有白有韩。有义山樊川。又有长吉卢仝。今特举曾南礼徐仲车。究竟以孟东野者。非为别寻一径。顶上有眼者。当镜镜相印也。(悟堂李雅诗思甚妙。来问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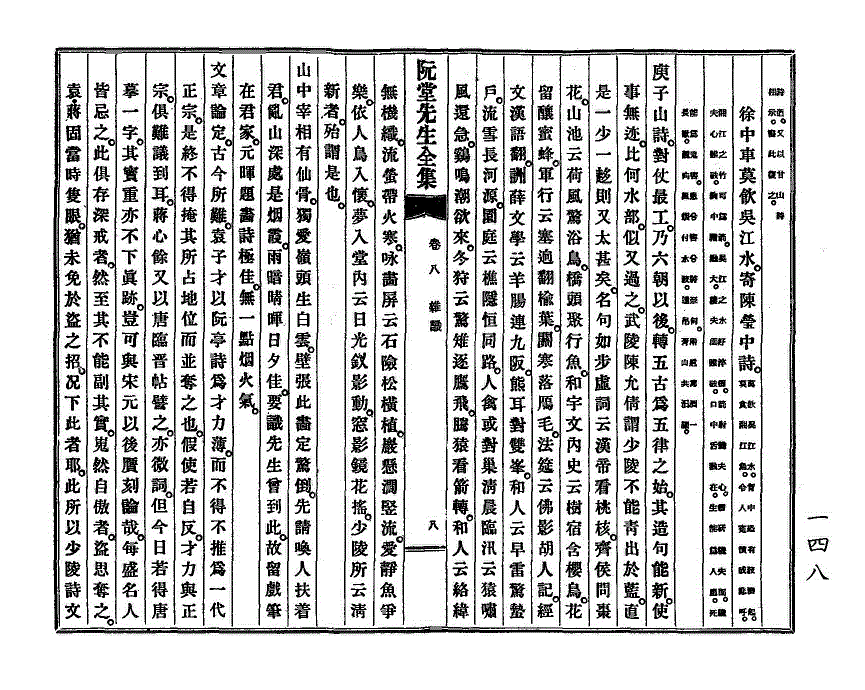 诗道。又以甘山诗相示。书此复之。)
诗道。又以甘山诗相示。书此复之。)徐中车莫饮吴江水。寄陈莹中诗。莫饮吴江水。胸中恐有波涛起。莫食湘江鱼。令人冤愤成悲呼。湘江之竹可为箭。吴江之水好淬剑。箭射谗夫心。剑研(一作斫)谗夫面。谗夫心虽破。胸中胆犹大。谗夫面虽破。口中舌犹在。生能为人患。死能为鬼害。患兮害兮将奈何。两卮薄酒一长歌。洒向风烟付水波。遣吊胥山共汨罗。
庾子山诗。对仗最工。乃六朝以后。转五古为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又过之。武陵陈允倩谓少陵不能青出于蓝。直是一少一趍则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虚词云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枣花。山池云荷风惊浴鸟。桥头聚行鱼。和宇文内史云树宿含樱鸟。花留酿蜜蜂。军行云塞迥翻榆叶。关寒落雁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记。经文汉语翻。詶薛文学云羊肠连九阪。熊耳对双峰。和人云早雷惊蛰户。流雪长河源。园庭云樵隐恒同路。人禽或对巢清晨临汛云猿啸风还急。鸡鸣潮欲来。冬狩云惊雉逐鹰飞。腾猿看箭转。和人云络纬无机织。流萤带火寒。咏画屏云石险松横植。岩悬涧竖流。爱静鱼争乐。依人鸟入怀。梦入堂内云日光钗影动。窗影镜花摇。少陵所云清新者。殆谓是也。
山中宰相有仙骨。独爱岭头生白云。壁张此画定惊倒。先请唤人扶着君。乱山深处是烟霞。雨暗晴晖日夕佳。要识先生曾到此。故留戏笔在君家。元晖题画诗极佳。无一点烟火气。
文章论定。古今所难。袁子才以阮亭诗为才力薄。而不得不推为一代正宗。是终不得掩其所占地位而并夺之也。假使若自反。才力与正宗。俱难议到耳。蒋心馀又以唐临晋帖譬之。亦微词。但今日若得唐摹一字。其宝重亦不下真迹。岂可与宋元以后赝刻论哉。每盛名人皆忌之。此俱存深戒者。然至其不能副其实。嵬然自傲者。盗思夺之。袁,蒋固当时只眼。犹未免于盗之招。况下此者耶。此所以少陵诗文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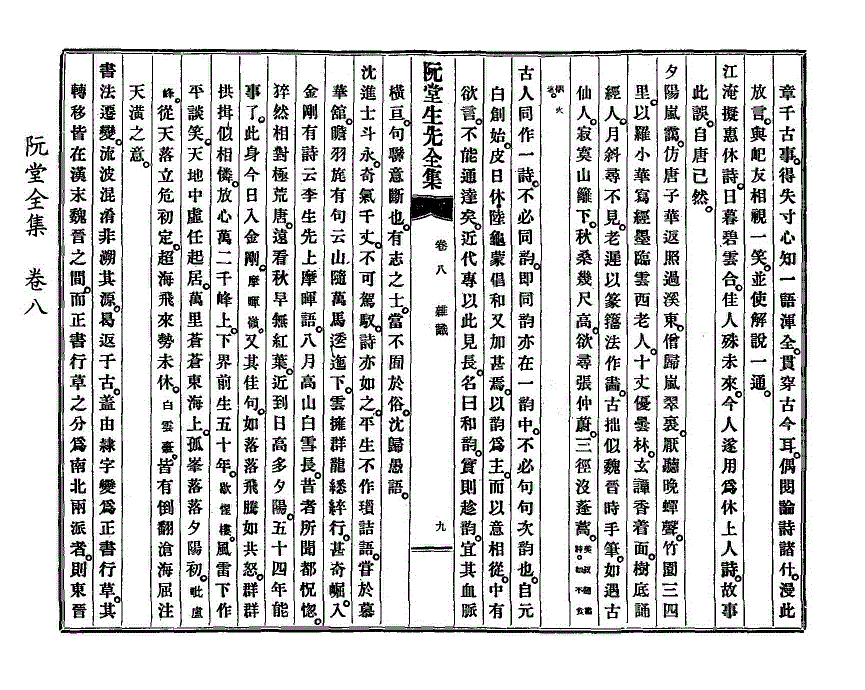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语浑全。贯穿古今耳。偶阅论诗诸什。漫此放言。与屺友相视一笑。并使解说一通。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语浑全。贯穿古今耳。偶阅论诗诸什。漫此放言。与屺友相视一笑。并使解说一通。江淹拟惠休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此误。自唐已然。
夕阳岚霭。仿唐子华返照过溪东。僧归岚翠里。厌听晚蝉声。竹园三四里。以罗小华写经墨临云西老人。十丈优昙林。玄谭香着面。树底诵经人。月斜寻不见。老迟以篆籀法作画。古拙似魏晋时手笔。如遇古仙人。寂寞山篱下。秋桑几尺高。欲寻张仲蔚。三径没蓬蒿。(美叔题画诗。如不食烟火者。)
古人同作一诗。不必同韵。即同韵亦在一韵中。不必句句次韵也。自元白创始。皮日休,陆龟蒙倡和又加甚焉。以韵为主。而以意相从。中有欲言。不能通达矣。近代专以此见长。名曰和韵。实则趁韵。宜其血脉横亘。句联意断也。有志之士。当不囿于俗。沈归愚语。
沈进士斗永。奇气千丈。不可驾驭。诗亦如之。平生不作琐诘语。尝于慕华馆。瞻羽旄有句云山随万马逶迤下。云拥群龙𦄵綷行。甚奇崛。入金刚有诗云李生先上摩晖语。八月高山白雪长。昔者所闻都恍惚。猝然相对极荒唐。远看秋早无红叶。近到日高多夕阳。五十四年能事了。此身今日入金刚。(摩晖岭。)又其佳句。如落落飞腾如共怒。群群拱揖似相怜。放心万二千峰上。下界前生五十年。(歇惺楼。)风雷下作平谈笑。天地中虚任起居。万里苍苍东海上。孤峰落落夕阳初。(毗卢峰。)从天落立危初定。超海飞来势未休。(白云台。)皆有倒翻沧海屈注天潢之意。
书法迁变。流波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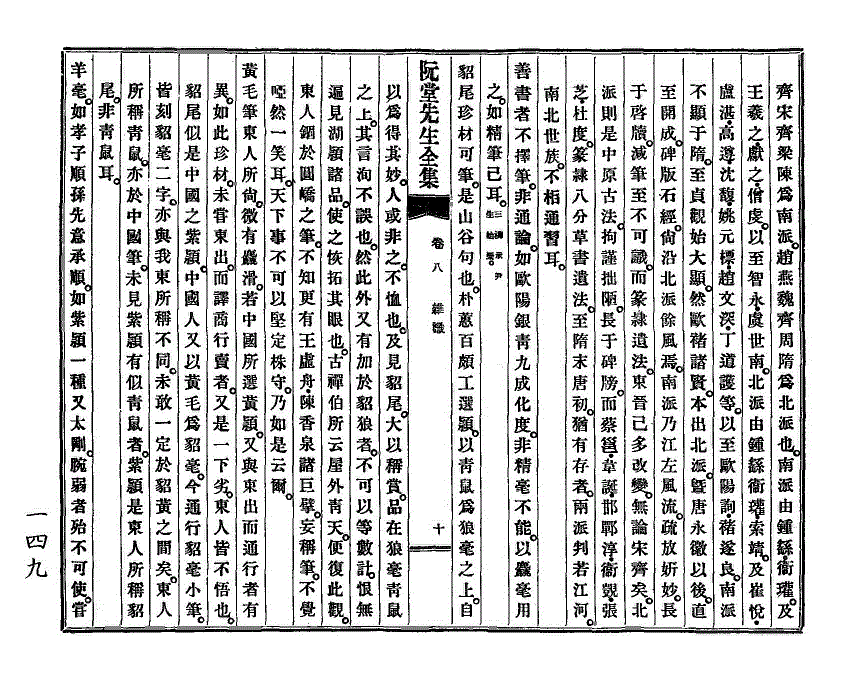 齐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暨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耳。
齐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暨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耳。善书者不择笔。非通论。如欧阳银青九成化度。非精毫不能。以粗毫用之。如精笔已耳。(三渊示尹生始荣。)
貂尾珍材可笔。是山谷句也。朴蕙百颇工选颖。以青鼠为狼毫之上。自以为得其妙。人或非之。不恤也。及见貂尾。大以称赏。品在狼毫青鼠之上。其言洵不误也。然此外又有加于貂狼者。不可以等数计。恨无遍见湖颖诸品。使之恢拓其眼也。古禅伯所云屋外青天。便复此观。东人锢于圆峤之笔。不知更有王虚舟,陈香泉诸巨擘。妄称笔。不觉哑然一笑耳。天下事不可以坚定株守。乃如是云尔。
黄毛笔东人所尚。微有粗滑。若中国所选黄颖。又与东出而通行者有异。如此珍材。未尝东出。而译商行卖者。又是一下劣。东人皆不悟也。貂尾似是中国之紫颖。中国人又以黄毛为貂毫。今通行貂毫小笔。皆刻貂毫二字。亦与我东所称不同。未敢一定于貂黄之间矣。东人所称青鼠。亦于中国笔。未见紫颖有似青鼠者。紫颖是东人所称貂尾。非青鼠耳。
羊毫。如孝子顺孙先意承顺。如紫颖一种又太刚。腕弱者殆不可使。尝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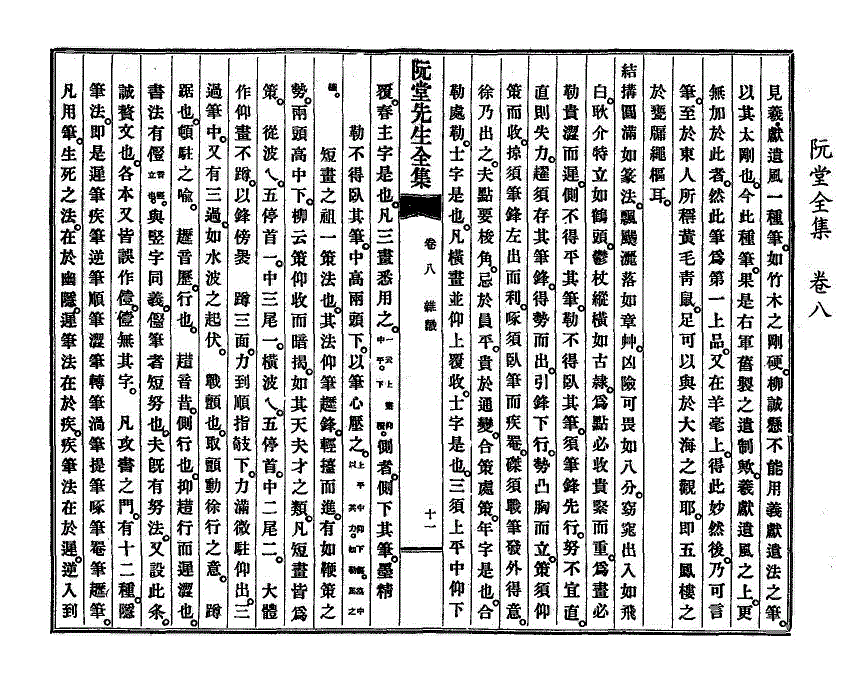 见羲,献遗风一种笔。如竹木之刚硬。柳诚悬不能用羲献遗法之笔。以其太刚也。今此种笔。果是右军旧制之遗制欤。羲献遗风之上。更无加于此者。然此笔为第一上品。又在羊毫上。得此妙然后。乃可言笔。至于东人所称黄毛青鼠。足可以与于大海之观耶。即五凤楼之于瓮牖绳枢耳。
见羲,献遗风一种笔。如竹木之刚硬。柳诚悬不能用羲献遗法之笔。以其太刚也。今此种笔。果是右军旧制之遗制欤。羲献遗风之上。更无加于此者。然此笔为第一上品。又在羊毫上。得此妙然后。乃可言笔。至于东人所称黄毛青鼠。足可以与于大海之观耶。即五凤楼之于瓮牖绳枢耳。结搆圆满如篆法。飘飏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杖纵横如古隶。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侧不得平其笔。勒不得卧其笔。须笔锋先行。努不宜直。直则失力。趯须存其笔锋。得势而出。引锋下行。势凸胸而立。策须仰策而收。掠须笔锋左出而利。啄须卧笔而疾罨。磔须战笔发外得意。徐乃出之。夫点要梭角。忌于员平。贵于通变。合策处策。年字是也。合勒处勒。士字是也。凡横画并仰上覆收。士字是也。三须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画悉用之。(一云上画仰中平。下▣覆。)侧者。侧下其笔。墨精。▣▣▣勒不得卧其笔。中高两头下。以笔心压之。(上平中仰下偃。空中以▣其力。如勒马之绳。)▣▣短画之祖一策法也。其法仰笔䟐锋。轻抬而进。有如鞭策之势。两头高中下。柳云策仰收而暗揭。如其天夫才之类。凡短画皆为策。 从波乀。五停首一。中三尾一。横波乀。五停首。中二尾二。 大体作仰画不蹲。以锋傍裹▣蹲三面。力到顺指攲下。力满微驻仰出。三过笔中。又有三过。如水波之起伏。 战颤也。取颤动徐行之意。 蹲踞也。顿驻之喻。 䟐音历。行也。 趞音昔。侧行也。抑趞行而迟涩也。书法有𠐊(音竖。立也。)与竖字同义。𠐊笔者短努也。夫既有努法。又设此条。诚赘文也。各本又皆误作𠍼。𠍼无其字。 凡攻书之门。有十二种。隐笔法。即是迟笔疾笔逆笔顺笔涩笔转笔涡笔提笔啄笔罨笔䟐笔。凡用笔。生死之法。在于幽隐。迟笔法在于疾。疾笔法在于迟。逆入到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0L 页
 出。取势加▣。诊候调停。其于得妙。须在功深。草草求▣难得。▣▣一字。八面流通为内气。一篇章法照应为外气。内气言笔画疏𡶇轻重肥瘦。若平板散涣。何气之有。外气言一篇有虚实疏密管束。接上递下。错综映带。第一字不可移至第二字。第二行不可移至第一行。
出。取势加▣。诊候调停。其于得妙。须在功深。草草求▣难得。▣▣一字。八面流通为内气。一篇章法照应为外气。内气言笔画疏𡶇轻重肥瘦。若平板散涣。何气之有。外气言一篇有虚实疏密管束。接上递下。错综映带。第一字不可移至第二字。第二行不可移至第一行。布白有三。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间之布白。初学皆须停匀。既知停匀。斜正疏密。错落其间。字资于墨。墨为字之血肉。用力在笔尖。为字之筋。有筋者顾眄生情。血脉流动。如游丝一道盘旋不断。有点画处在画中。无点画处。亦隐隐相贯。重叠牵连。其间庶无呆板散涣之病。书法论云正书用行草意。行书用正书法是也。盖行草用意。有笔墨可寻。行草多牵丝。至真书多使转。合一不二。神气相贯。盖真书多用使转。使转者无形迹。牵丝者有形迹之使转。使转者无形迹之牵丝也。牵丝使转合之然后为完法耳。
笔之轻者为阳。重者为阴。凡字中有两直者。宜左细右粗。字中之柱宜粗。馀俱宜细。此分阴阳之法耳。
正锋偏锋之说。古本无之。近来专欲攻祝京兆。故借此为谈。正以立骨。偏以取态。自不容已。
书家虽贵藏锋。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剸截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耳。
赵文敏善用笔。所使笔有宛转如意者。辄剖之取其精毫。别贮之。凡笔三管之精。令工总缚一管。真草巨细。投之无不可。终岁无敞耳。
书家谓作真字。能寓篆籀法则高古今。
书法与诗品画随。同一妙境。如西京古隶之斩钉截铁。凶险可畏。即积健为雄之义。青春鹦鹉。插花舞女。援镜笑春之义。游天戏海。即前招三辰后引风凰之义。无不与诗通。并不外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一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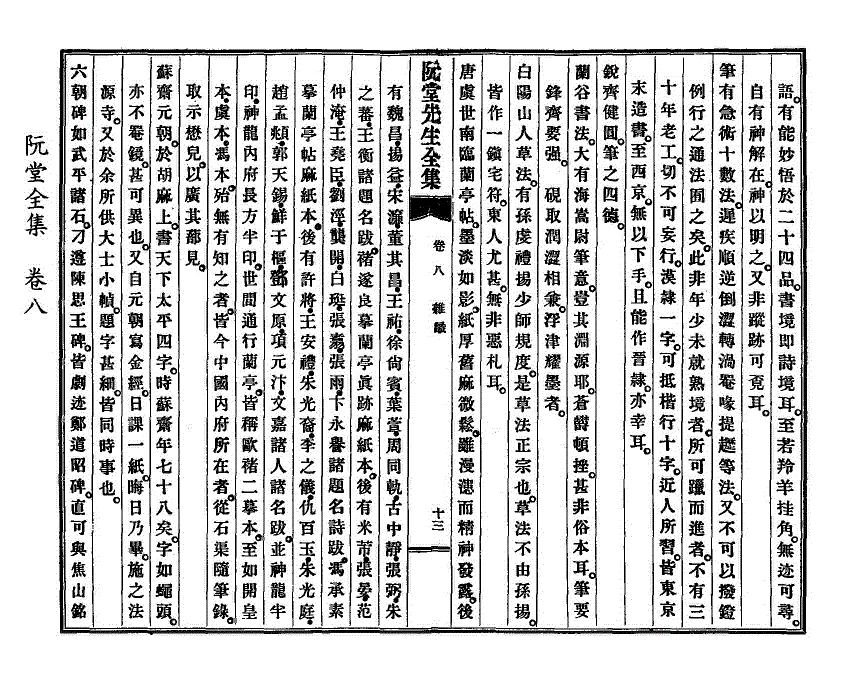 语。有能妙悟于二十四品。书境即诗境耳。至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自有神解在。神以明之。又非踪迹可觅耳。
语。有能妙悟于二十四品。书境即诗境耳。至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自有神解在。神以明之。又非踪迹可觅耳。笔有急术十数法。迟疾顺逆倒涩转涡罨喙提䟐等法。又不可以拨镫例行之通法囿之矣。此非年少未就熟境者。所可躐而进者。不有三十年老工。切不可妄行。漠隶一字。可抵楷行十字。近人所习。皆东京末造书。至西京。无以下手。且能作晋隶。亦幸耳。
锐齐健圆。笔之四德。
兰谷书法。大有海嵩尉笔意。岂其渊源耶。苍郁顿挫。甚非俗本耳。笔要锋齐要强。 砚取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
白阳山人草法。有孙虔礼扬少师规度。是草法正宗也。草法不由孙扬。皆作一镇宅符。东人尤甚。无非恶札耳。
唐虞世南临兰亭帖。墨淡如影。纸厚旧麻微松。虽漫漶而精神发露。后有魏昌,扬益,宋濂,董其昌,王祐,徐尚宾,叶萱,周同轨,古中静,张弼,朱之蕃,王衡诸题名跋。褚遂良摹兰亭真迹麻纸本。后有米芾,张晏,范仲淹,王尧臣,刘泾,龚开,白珽,张翥,张雨,卞永誉诸题名诗跋。冯承素摹兰亭帖麻纸本。后有许将,王安礼,朱光裔,李之仪,仇百玉,朱光庭,赵孟頫,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项元汴,文嘉诸人诸名跋。并神龙半印。神龙内府长方半印。世间通行兰亭。皆称欧褚二摹本。至如开皇本,虞本,冯本。殆无有知之者。皆今中国内府所在者。从石渠随笔录。取示懋儿。以广其蔀见。
苏斋元朝。于胡麻上。书天下太平四字。时苏斋年七十八矣。字如蝇头。亦不罨镜。甚可异也。又自元朝写金经。日课一纸。晦日乃毕。施之法源寺。又于余所供大士小帧。题字甚细。皆同时事也。
六朝碑如武平诸石。刁遵陈思王碑。皆剧迹郑道昭碑。直可与焦山铭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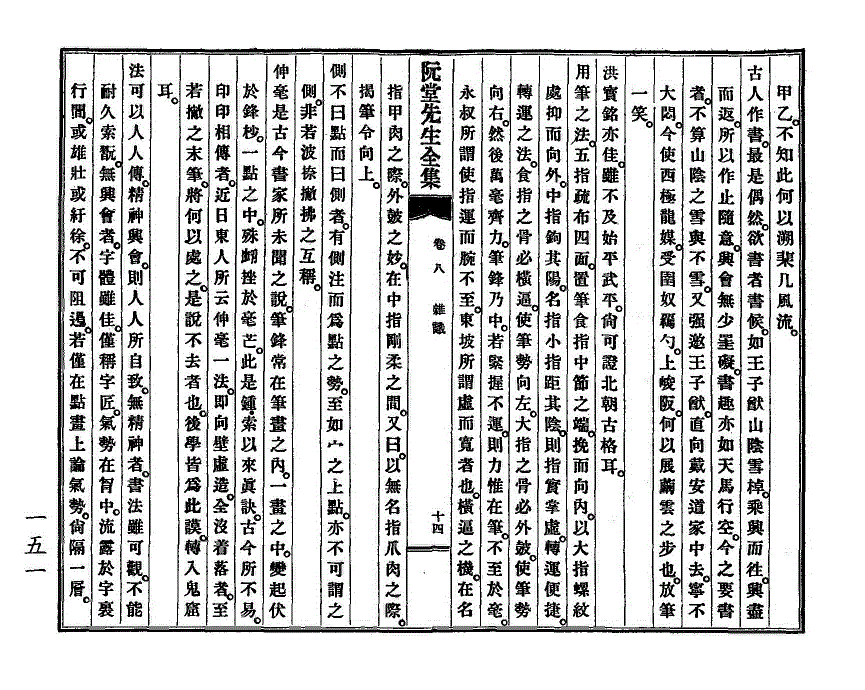 甲乙。不知此何以溯棐几风流。
甲乙。不知此何以溯棐几风流。古人作书。最是偶然。欲书者书候。如王子猷山阴雪棹。乘兴而往。兴尽而返。所以作止随意。兴会无少挂碍。书趣亦如天马行空。今之要书者。不算山阴之雪与不雪。又强邀王子猷。直向戴安道家中去。宁不大闷。今使西极龙媒。受圉奴羁勺。上峻阪。何以展茧云之步也。放笔一笑。
洪宝铭亦佳。虽不及始平武平。尚可證北朝古格耳。
用笔之法。五指疏布四面。置笔食指中节之端。挽而向内。以大指螺纹处抑而向外。中指钩其阳。名指小指距其阴。则指实掌虚。转运便捷。转运之法。食指之骨必横逼。使笔势向左。大指之骨必外鼓。使笔势向右。然后万毫齐力。笔锋乃中。若紧握不运。则力惟在笔。不至于毫。永叔所谓使指运而腕不至。东坡所谓虚而宽者也。横逼之机。在名指甲肉之际。外鼓之妙。在中指刚柔之间。又曰。以无名指爪肉之际。揭笔令向上。
侧不曰点而曰侧者。有侧注而为点之势。至如定上点。亦不可谓之侧。非若波捺撇拂之互称。
伸毫是古今书家所未闻之说。笔锋常在笔画之内。一画之中。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中。殊衄挫于毫芒。此是钟,索以来真诀。古今所不易。印印相传者。近日东人所云伸毫一法。即向壁虚造。全没着落者。至若撇之末笔。将何以处之。是说不去者也。后学皆为此谟。转入鬼窟耳。
法可以人人传。精神兴会。则人人所自致。无精神者。书法虽可观。不能耐久索玩。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字匠。气势在胸中。流露于字里行间。或雄壮或纡徐。不可阻遏。若仅在点画上论气势。尚隔一层。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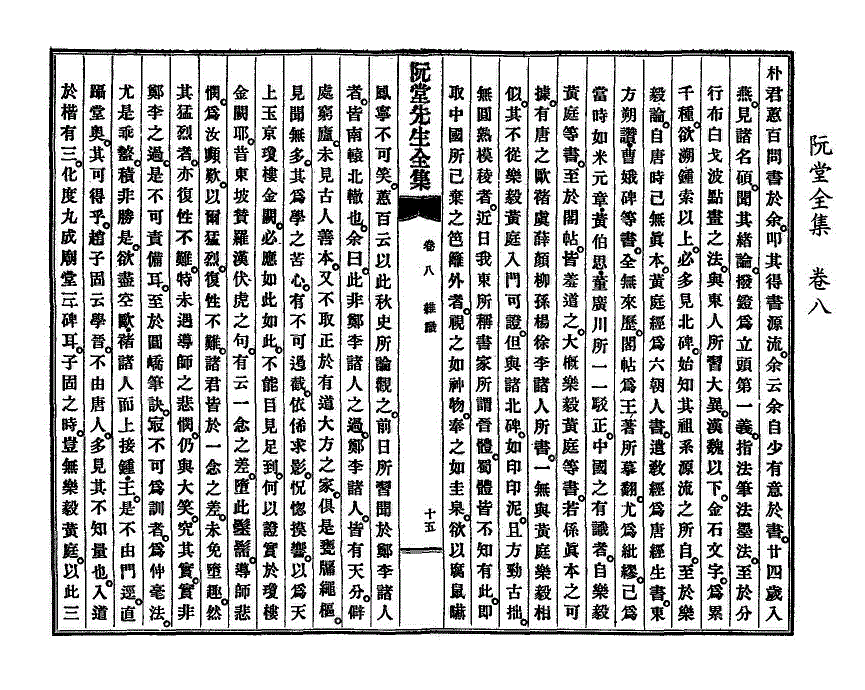 朴君蕙百问书于余。叩其得书源流。余云余自少有意于书。廿四岁入燕。见诸名硕。闻其绪论。拨镫为立头第一义。指法笔法墨法。至于分行布白戈波点画之法。与东人所习大异。汉魏以下。金石文字。为累千种。欲溯钟索以上。必多见北碑。始知其祖系源流之所自。至于乐毅论。自唐时已无真本。黄庭经为六朝人书。遗教经为唐经生书。东方朔赞,曹娥碑等书。全无来历。阁帖为王著所摹翻。尤为纰缪。已为当时如米元章,黄伯思,董广川所一一驳正。中国之有识者。自乐毅黄庭等书。至于阁帖。皆羞道之。大概乐毅黄庭等书。若系真本之可据。有唐之欧褚虞薛颜柳孙杨徐李诸人所书。一无与黄庭乐毅相似。其不从乐毅黄庭入门可證。但与诸北碑。如印印泥。且方劲古拙。无圆熟模棱者。近日我东所称书家所谓晋体。蜀体皆不知有此。即取中国所已弃之笆篱外者。视之如神物。奉之如圭臬。欲以腐鼠吓凤宁不可笑。蕙百云以此秋史所论观之。前日所习闻于郑李诸人者。皆南辕北辙也。余曰。此非郑李诸人之过。郑李诸人。皆有天分。僻处穷庐。未见古人善本。又不取正于有道大方之家。俱是瓮牖绳枢。见闻无多。其为学之苦心。有不可遏截。依俙求影。恍惚摸响。以为天上玉京琼楼金阙。必应如此如此。不能目见足到。何以證实于琼楼金阙耶。昔东坡赞罗汉伏虎之句。有云一念之差。堕此髬髵。导师悲悯。为汝嚬叹。以尔猛烈。复性不难。诸君皆于一念之差。未免堕趣。然其猛烈者。亦复性不难。特未遇导师之悲悯。仍与大笑。究其实。实非郑李之过。是不可责备耳。至于圆峤笔诀。最不可为训者。为伸毫法。尤是乖盩。积非胜是。欲尽空欧,褚诸人而上接钟,王。是不由门径。直蹑堂奥。其可得乎。赵子固云学晋。不由唐人。多见其不知量也。入道于楷有三。化度九成庙堂三碑耳。子固之时。岂无乐毅黄庭。以此三
朴君蕙百问书于余。叩其得书源流。余云余自少有意于书。廿四岁入燕。见诸名硕。闻其绪论。拨镫为立头第一义。指法笔法墨法。至于分行布白戈波点画之法。与东人所习大异。汉魏以下。金石文字。为累千种。欲溯钟索以上。必多见北碑。始知其祖系源流之所自。至于乐毅论。自唐时已无真本。黄庭经为六朝人书。遗教经为唐经生书。东方朔赞,曹娥碑等书。全无来历。阁帖为王著所摹翻。尤为纰缪。已为当时如米元章,黄伯思,董广川所一一驳正。中国之有识者。自乐毅黄庭等书。至于阁帖。皆羞道之。大概乐毅黄庭等书。若系真本之可据。有唐之欧褚虞薛颜柳孙杨徐李诸人所书。一无与黄庭乐毅相似。其不从乐毅黄庭入门可證。但与诸北碑。如印印泥。且方劲古拙。无圆熟模棱者。近日我东所称书家所谓晋体。蜀体皆不知有此。即取中国所已弃之笆篱外者。视之如神物。奉之如圭臬。欲以腐鼠吓凤宁不可笑。蕙百云以此秋史所论观之。前日所习闻于郑李诸人者。皆南辕北辙也。余曰。此非郑李诸人之过。郑李诸人。皆有天分。僻处穷庐。未见古人善本。又不取正于有道大方之家。俱是瓮牖绳枢。见闻无多。其为学之苦心。有不可遏截。依俙求影。恍惚摸响。以为天上玉京琼楼金阙。必应如此如此。不能目见足到。何以證实于琼楼金阙耶。昔东坡赞罗汉伏虎之句。有云一念之差。堕此髬髵。导师悲悯。为汝嚬叹。以尔猛烈。复性不难。诸君皆于一念之差。未免堕趣。然其猛烈者。亦复性不难。特未遇导师之悲悯。仍与大笑。究其实。实非郑李之过。是不可责备耳。至于圆峤笔诀。最不可为训者。为伸毫法。尤是乖盩。积非胜是。欲尽空欧,褚诸人而上接钟,王。是不由门径。直蹑堂奥。其可得乎。赵子固云学晋。不由唐人。多见其不知量也。入道于楷有三。化度九成庙堂三碑耳。子固之时。岂无乐毅黄庭。以此三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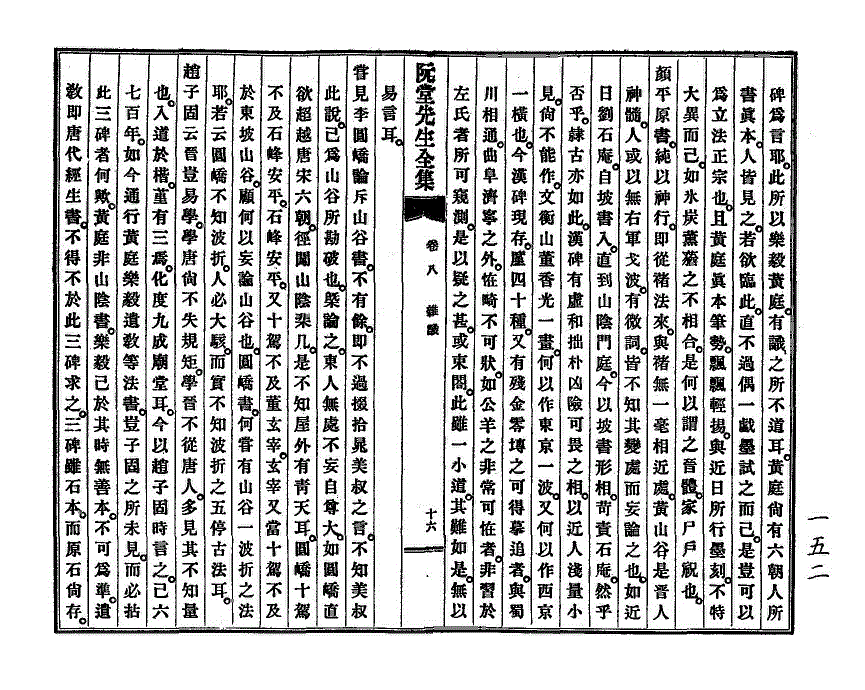 碑为言耶。此所以乐毅黄庭。有识之所不道耳。黄庭尚有六朝人所书真本。人皆见之。若欲临此。直不过偶一戏墨试之而已。是岂可以为立法正宗也。且黄庭真本笔势。飘飘轻扬。与近日所行墨刻。不特大异而已。如冰炭薰莸之不相合。是何以谓之晋体。家尸户祝也。
碑为言耶。此所以乐毅黄庭。有识之所不道耳。黄庭尚有六朝人所书真本。人皆见之。若欲临此。直不过偶一戏墨试之而已。是岂可以为立法正宗也。且黄庭真本笔势。飘飘轻扬。与近日所行墨刻。不特大异而已。如冰炭薰莸之不相合。是何以谓之晋体。家尸户祝也。颜平原书。纯以神行。即从褚法来。与褚无一毫相近处。黄山谷是晋人神髓。人或以无右军戈波。有微词。皆不知其变处而妄论之也。如近日刘石庵。自坡书入。直到山阴门庭。今以坡书形相。苟责石庵。然乎否乎。隶古亦如此。汉碑有虚和拙朴凶险可畏之相。以近人浅量小见。尚不能作。文衡山董香光一画。何以作东京一波。又何以作西京一横也。今汉碑现存。廑四十种。又有残金零塼之可得摹追者。与蜀川相通。曲阜济宁之外。怪畸不可状。如公羊之非常可怪者。非习于左氏者所可窥测。是以疑之甚。或束閤。此虽一小道。其难如是。无以易言耳。
尝见李圆峤论斥山谷书。不有馀。即不过掇拾晁美叔之言。不知美叔此说。已为山谷所勘破也。槩论之。东人无处不妄自尊大。如圆峤直欲超越唐宋六朝。径闯山阴棐几。是不知屋外有青天耳。圆峤十驾不及石峰安平。石峰安平。又十驾不及董玄宰。玄宰又当十驾不及于东坡山谷。顾何以妄论山谷也。圆峤书。何尝有山谷一波折之法耶。若云圆峤不知波折。人必大骇。而实不知波折之五停古法耳。
赵子固云晋岂易学。学唐尚不失规矩。学晋不从唐人。多见其不知量也。入道于楷。堇有三焉。化度九成庙堂耳。今以赵子固时言之。已六七百年。如今通行黄庭乐毅遗教等法书。岂子固之所未见。而必拈此三碑者何欤。黄庭非山阴书。乐毅已于其时无善本。不可为准。遗教即唐代经生书。不得不于此三碑求之。三碑虽石本。而原石尚存。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3H 页
 下真迹一等。非后世石刻之转相摸翻者可比也。吾东书法。罗丽二时。专习欧体。今存旧碑。尚可溯得其一二。自本 朝来。皆趍松雪一路。然如申,成诸公所书门榜。雄奇古雅。大有旧法。以至石峰。而虽有松雪气味。亦恪遵古式。嗣后自以为极力挽古者。辄皆动称黄庭乐毅晋体。未知黄庭乐毅竟是何本欤。遂至圆峤。又书抹古来遗规。臆造一法。执笔不讲悬臂。拨镫结字。不知左取上齐右取下齐等法之自古不敢易者。一世陆沉。殆无迥悟者。是书家之一大变耳。学书者知晋之未易学。而由唐人为入晋径路。庶无误矣。古贤作字。未有不腾空直下。能造入神品者。非悬臂不能。悬臂则在空际旋转。随其到处。极肥至瘦。皆成妙趣。得天司寇。学书先悬臂。画圆圈三个月。待得圈子圆净纯熟。则用笔自然遒劲。圆转裕如。下笔作字。自无扁锋。但圈子总不得参以指运。
下真迹一等。非后世石刻之转相摸翻者可比也。吾东书法。罗丽二时。专习欧体。今存旧碑。尚可溯得其一二。自本 朝来。皆趍松雪一路。然如申,成诸公所书门榜。雄奇古雅。大有旧法。以至石峰。而虽有松雪气味。亦恪遵古式。嗣后自以为极力挽古者。辄皆动称黄庭乐毅晋体。未知黄庭乐毅竟是何本欤。遂至圆峤。又书抹古来遗规。臆造一法。执笔不讲悬臂。拨镫结字。不知左取上齐右取下齐等法之自古不敢易者。一世陆沉。殆无迥悟者。是书家之一大变耳。学书者知晋之未易学。而由唐人为入晋径路。庶无误矣。古贤作字。未有不腾空直下。能造入神品者。非悬臂不能。悬臂则在空际旋转。随其到处。极肥至瘦。皆成妙趣。得天司寇。学书先悬臂。画圆圈三个月。待得圈子圆净纯熟。则用笔自然遒劲。圆转裕如。下笔作字。自无扁锋。但圈子总不得参以指运。钟鼎古文。皆隶法所出来处。学隶者不知此。便溯流忘源耳。
吾辈学汉隶字。皆不免作唐隶。然唐隶亦难及。唐隶不止一明皇孝经而已。汉碑所无之字。不可妄造。若于唐碑有之。尚可依样为之。不如篆体之至严。篆字决不可沿唐。虽李少温。断不可从耳。
姜白石所藏定武兰亭。为赵子固落水本。苏米斋手模。无毫釐差讹。又为姜开阳刻于山阴。兰亭之于姜氏。大墨缘耳。
书家必以右军父子为准则。然二王书。世无传本。真迹之尚存。惟快雪时晴。与太令送梨帖。都计不过百字。千载之下。追溯棐几家风。止此而已。亦皆入内府。非外人所可见。如刘摹章刻。尚是一翻者。摹法刻法。已不及宋元。又何论于粱摹唐刻也。六朝碑版。颇有传本。欧褚皆从此出。然宋元诸公。无甚称道者。以其二王真书。犹未尽泯。如今时也。今人当从北碑下手。然后可以入道耳。焦山鹤铭。即六朝人书。又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3L 页
 如郑道昭诸石刻皆可观。如黄山谷屡及焦山。而未尝举郑。亦可异。
如郑道昭诸石刻皆可观。如黄山谷屡及焦山。而未尝举郑。亦可异。衡方碑夏承碑上送。夏承碑原石已不存。皆此重刻本通行耳。
白下书出于文衡山。世皆不知。且白下亦不自言。文书小楷赤壁赋墨拓一本东出。白下专心学之。其短竖之上礼下杀处。即其所得法。而文书清婉劲利。白下微钝差肥。且文之结搆。皆合于欧褚颜柳相传之旧式白下皆漫书之一字之内。逐其横竖点捺砌凑之。然其天品甚异加之人工。终成一家数者以其不以衡山卑近而俯首学习不以鹜远自大。如后来妄称钟王也。其大楷之金石碑版前面字。专法坡公表忠碑。其半草以米南宫为归。并不出宋人圈子外。即其识力大有商量处。其门下得髓。以圆峤为第一。圆峤初年所作楷字。即与师门无少异。如一手。实不知但从师门所书学之。曾不一叩师门之所出。又何哉。师门亦不告其所出。又何哉。抑或师道甚严。不敢妄请欤。师门之不以告者。即又不示璞之义欤。白下用羊毫笔。徐丹阳尝云见师门所书中国大毫白如雪。竟不知为何笔。亦不敢请。盖古人师道之严亦可见。徐李皆其高足。李又传其笔。皆不知羊毫。虽知之。白下能使得他。皆笔性之所不合耳。
豹庵书即出于褚河南。亦不言所自如白下。古人多如是处。
米南宫书出于罗让。而世但知米。不知有罗。兰亭一为欧摹。一为褚临。欧有欧体。褚有褚体。世但知为山阴。而反不知是欧是褚。若以欧褚书为言。虽九成化度三龛圣教。举皆忽之。中国人未尝如此。东人偏欲抹摋之。如宋元诸人。必欲针砭西京东京。直为超趣而上之。其实目未尝见化度三龛。公然虚喝以傲耳。米以褚临为天下第一。其时不少定武。而必以褚重。米之鉴识。当有所参證。非后人浅量可测。如黄山谷又表气定武。姜白石,赵彝斋。皆以定武为真。后世之动称定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4H 页
 武。亦以是耳。桑俞诸鉴赏。又不专以定武为归。并举褚本。
武。亦以是耳。桑俞诸鉴赏。又不专以定武为归。并举褚本。乐毅论之梁摹唐刻。已自北宋时绝罕。近世所行俗本。是王著书也。东人尤无鉴别。认以棐几真影。童习白纷。竟不觉悟。如蔡九峰所传书古文。皆不知为梅伪也。书画一道耳。未闻画家必上探曹不兴,张僧繇。若得王右丞江干雪霁传本。吴道玄菩萨天王摹笔。奉之如天球弘璧。如宋之燕文贵易元吉。为希世之宝。元之四大家。(赵松雪,倪云林,黄大痴,王蒙。)亦难得其真本。虽明之沈石田刘完庵,文衡山,董香光之至近。而视同金科玉条。书则不然。必以钟王为准。非是辄皆忽之。如欧褚皆晋人神髓。而李圆峤以方板眇之。谓之右军不是书之科。不自觉其平生所习。乃王著书乐毅论也。董香光是书家一大结局。举抹倒之。中国人以董临兰亭诗。入于兰亭八柱帖内。有若嫡派真脉之相传。东人眼光。有甚过于中国赏鉴而然欤。多见其不知量也。若使圆峤低首向畅整敬客书学习。以其天品。溯欧褚之不难。又不必深加苛责也。二王真迹之至今尚存于中国者。有若右军快雪时晴。袁生等帖。大令之送梨帖。皆其寻常阅过。寻常摹习。又如虞摹兰亭。褚本兰亭。冯之兰亭。陆之兰亭。开皇兰亭。东人何尝梦及。不知此个道理。一以迷误不返。执三钱鸡毛。动称晋体。其所云晋体。竟果何本。不过是王者乐毅论耳。宁不可叹。偶阅孙过庭狮子赋,林藻深慰帖。不觉神飞仍书。孙林即晋人规则也。欲学草法。不由孙之门径。又是村肆酒壁。一镇宅符之恶札耳。
胸中有五千字。始可以下笔。书品画品。皆超出一等。不然。只俗匠魔界而已耳。
欧书如奇花初胎。含蓄不露。邕师塔铭。其神行幻现处。人无以觅影寻迹。褚之三龛。孟法师圣教等书。如瞻岁新。如逢花开。无不流行。变现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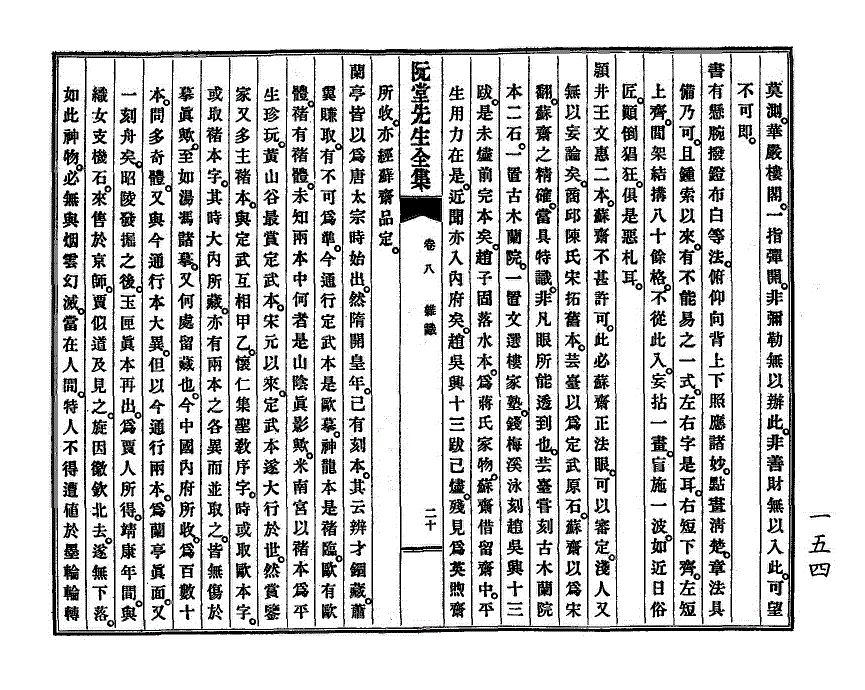 莫测。华严楼阁。一指弹开。非弥勒无以办此。非善财无以入此。可望不可即。
莫测。华严楼阁。一指弹开。非弥勒无以办此。非善财无以入此。可望不可即。书有悬腕拨镫布白等法。俯仰向背上下照应诸妙。点画清楚。章法具备乃可。且钟索以来。有不能易之一式。左右字是耳。右短下齐。左短上齐。间架结搆八十馀格。不从此入。妄拈一画。盲施一波。如近日俗匠。颠倒猖狂。俱是恶札耳。
颖井王文惠二本。苏斋不甚许可。此必苏斋正法眼。可以审定。浅人又无以妄论矣。商邱陈氏宋拓旧本。芸台以为定武原石。苏斋以为宋翻。苏斋之精确。当具特识。非凡眼所能透到也。芸台尝刻古木兰院本二石。一置古木兰院。一置文选楼家塾。钱梅溪泳刻赵吴兴十三跋。是未烬前完本矣。赵子固落水本。为蒋氏家物。苏斋借留斋中。平生用力在是。近闻亦入内府矣。赵吴兴十三跋已烬。残见为英煦斋所收。亦经藓斋品定。
兰亭皆以为唐太宗时始出。然隋开皇年。已有刻本。其云辨才锢藏。萧翼赚取。有不可为准。今通行定武本是欧摹。神龙本是褚临。欧有欧体。褚有褚体。未知两本中何者是山阴真影欤。米南宫以褚本为平生珍玩。黄山谷最赏定武本。宋元以来。定武本遂大行于世。然赏鉴家又多主褚本。与定武互相甲乙。怀仁集圣教序字。时或取欧本字。或取褚本字。其时大内所藏。亦有两本之各异而并取之。皆无伤于摹真欤。至如汤冯诸摹。又何处留藏也。今中国内府所收。为百数十本。问多奇体。又与今通行本大异。但以今通行两本。为兰亭真面。又一刻舟矣。昭陵发掘之后。玉匣真本再出。为贾人所得。靖康年间。与织女支机石。来售于京师。贾似道及见之。旋因徽饮北去。遂无下落。如此神物。必无与烟云幻灭。当在人间。特人不得遭值于墨轮轮转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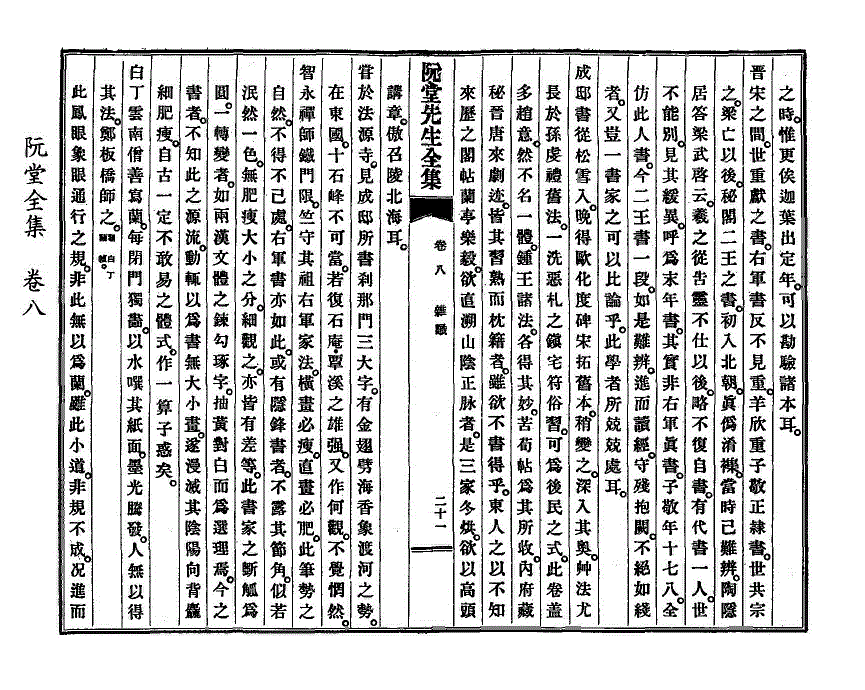 之时。惟更俟迦叶出定年。可以勘验诸本耳。
之时。惟更俟迦叶出定年。可以勘验诸本耳。晋宋之间。世重献之书。右军书反不见重。羊欣重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梁亡以后。秘阁二王之书。初入北朝。真伪淆杂。当时已难辨。陶隐居答梁武启云。羲之从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有代书一人。世不能别。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其实非右军真书。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今二王书一段。如是难辨。进而读经。守残抱阙。不绝如线者。又岂一书家之可以比论乎。此学者所兢兢处耳。
成邸书从松雪入。晚得欧化度碑宋拓旧本。稍变之。深入其奥。草法尤长于孙虔礼旧法。一洗恶札之镇宅符俗习。可为后民之式。此卷盖多赵意。然不名一体。钟王诸法。各得其妙。苦荀帖为其所收。内府藏秘晋唐来剧迹。皆其习熟而枕籍者。虽欲不书得乎。东人之以不知来历之阁帖兰亭乐毅。欲直溯山阴正脉者。是三家冬烘。欲以高头讲章。傲召陵北海耳。
尝于法源寺。见成邸所书刹那门三大字。有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之势。在东国。十石峰不可当。若复石庵,覃溪之雄强。又作何观。不觉惘然。
智永禅师铁门限。竺守其祖右军家法。横画必瘦。直画必肥。此笔势之自然。不得不已处。右军书亦如此。或有隐锋书者。不露其节角。似若泯然一色。无肥瘦大小之分。细观之。亦皆有差等。此书家之斲觚为圆。一转变者。如两汉文体之鍊勾琢字。抽黄对白而为选理焉。今之书者。不知此之源流。动辄以为书无大小画。遂漫灭其阴阳向背粗细肥瘦。自古一定不敢易之体式。作一算子惑矣。
白丁云南僧善写兰。每闭门独画。以水噀其纸面。墨光腾发。人无以得其法。郑板桥师之。(题白丁兰帧。)
此凤眼象眼通行之规。非此无以为兰。虽此小道。非规不成。况进而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5L 页
 大于是者乎。是以一叶一瓣。自欺不得。又不可以欺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是以写兰下手。当自无自欺始。
大于是者乎。是以一叶一瓣。自欺不得。又不可以欺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是以写兰下手。当自无自欺始。赵子固写兰。笔笔向左。苏斋老人屡称之。
元人作画。以枯墨起手。渐次积墨。未了之树。阘茸之山。皆从天机得之。大痴有大痴皴。云林有云林皴。非人力所假而为之。
静悟青绿三十年。以元人笔。运唐人气韵。作宋人丘壑。笔端有金刚杵。如天马行空。如天衣无缝。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开皇兰亭诗序墨拓卷。开皇十八年三月廿日刻。乃稧帖石刻之祖。南宋丞相游似景仁所藏。有赵孟吁,周驰,袁裒吾衍题识。后有游景仁,吴文贵,孙承泽,曹溶四跋。又有澄心堂晋府诸收藏印。景仁跋云右鬻者题曰定武。余既归乡。以往岁邓氏赵氏本较之。无分毫差。据此三本断缺处。与婺之梅花兰亭同其异者。婺本上下有界画。而此则无尔。此当为开皇本。而彼则再刻也。
白牧丹云神。仙队里风流易。富贵场中本色难。白桃花云后庭歌罢酲初醒。前度人来鬓已华。又亡息国因红粉累。避秦人是白衣尊。诗有不说理而真乃说理者。如唐人咏棋云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咏帆云恰认己身住。翻疑彼岸移。宋人君王若看貌。甘在象妃中。雪诗何由更得齐民煖。恨不偏于宿麦深。云诗无限早苗枯欲尽。悠悠閒处作奇峰。(示台济。)
洞庭橘唐金橘小橘金橘四品为上。别橘品最奇种最稀。不能充贡。山橘最多最下。青橘石金橘。皆味不佳。大橘未见。柑子橙子。皆不如中国日本产。乳柑稍爽亦酸。唐柚子烂熟经春者极甘爽。柑子无香。枳壳与青橘入药。
洞庭橘高家私园只二树。官园只一树。唐金橘官园只一树。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6H 页
 建初尺当省尺七寸五分。浙尺八寸四分。
建初尺当省尺七寸五分。浙尺八寸四分。钟索以下书家。皆无传诀。惟口口相授。至智永。始以永字八法。笔之于书。又有也字一法。然不专泥于窠臼。八法之转变为七十馀则。又有隐术十馀笔。非语言文字可得形容。神以明之耳。
元史太祖本纪及耶律楚材传。帝至东印度。驻铁门角端。见班师者。盖本于宋子贞所作楚材神道碑。不知太祖军踰雪山。止至北印度。何由遽及濒海之东印度。若铁门则未至雪山。距北印度尚远。考湛然集。楚材在西域十年。止驻寻思干城。纵或偶至铁门。无由至印度。神道碑欲归功楚材。故移印度之事铁门。以傅会之。不知种种不合。
蒙古源流云成吉思汗。将进征额纳特阿克。直抵齐塔纳凌岭之山脊。遇一独角兽。名曰赛鲁。奔至汗前。屈膝而叩。汗曰。彼额纳特阿克。乃古昔大圣降生之地。今奇兽至前。殆上天示意。遂振旅而还次。明言遇兽在雪山。非铁门。非东印度。且非因楚材之谏。盖楚材在西域十馀年。驻守寻思干城。即赛马尔罕城也。终身未至印度北之大雪山。后人作耶律神道碑者。必欲归功楚材。故移雪山之事于铁门。以迁就之。不知千里之谬。而元史因之。明史因之。
元太祖军踰雪山。追算端实。止至北印度。未亲至中印度。有长春西行记可證。若仅及铁门。则北印度尚未至。况能逾中印度而至濒海之东印度乎。此则万里之谬。亦始于耶律神道碑。而元史因之。明史因之。五印度之疆域。南印度以大海界之。西印度有红海地中海界之。古今截然不紊。惟东北二印度。陆地界淆各国。然东印度航海相通。商夷共习至。北印度则隔葱岭以西。中国西洋商旅皆不至。又元明后国名地名。与唐以前。不相贯串。所幸克什弥尔。为唐宋之迦湿弥罗国。千馀载不易。有大雪山界其北。得据为北印度之罽宾。
阮堂先生全集卷八 第 156L 页
 自元史以铁门为东印度。明史以赛马尔罕为古罽宾。重纰叠谬。从此棼起。不辟之则印度北境。终不可明。
自元史以铁门为东印度。明史以赛马尔罕为古罽宾。重纰叠谬。从此棼起。不辟之则印度北境。终不可明。汉时大月氏大夏境域。即赛马尔罕之域。兼今敖罕布哈尔爱乌罕诸部地。自嘉靖后入贡。一国称王。五十馀人。则已四分五裂。故今葱岭西。无复赛马尔罕之名。而图西域者向列其旧国。以统葱岭诸部。坤舆职方诸图,海国闻见录,庄氏地球图并同。殊非核实从今之义。故详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