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台山集卷二十 第 x 页
台山集卷二十(安东金迈淳德叟)
阙馀散笔
阙馀散笔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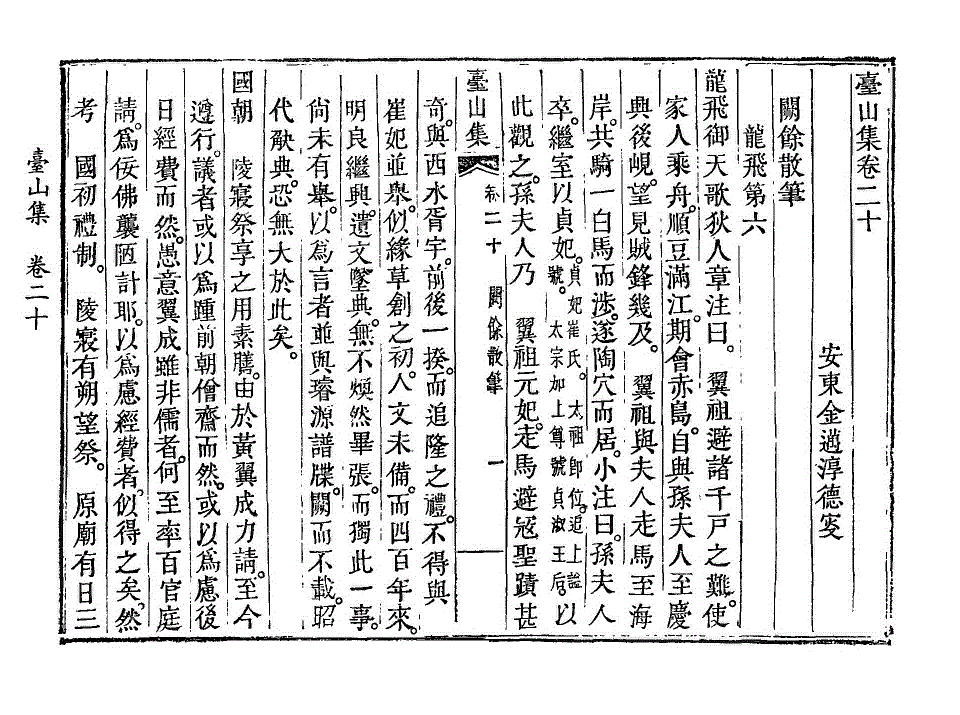 龙飞第六
龙飞第六龙飞御天歌狄人章注曰。 翼祖避诸千户之难。使家人乘舟。顺豆满江。期会赤岛。自与孙夫人至庆兴后岘。望见贼锋几及。 翼祖与夫人走马至海岸。共骑一白马而涉。遂陶穴而居。小注曰。孙夫人卒。继室以贞妃。(贞妃崔氏。 太祖即位。追上谥号 太宗加上尊号贞淑王后。)以此观之。孙夫人乃 翼祖元妃。走马避寇圣迹甚奇。与西水胥宇。前后一揆。而追隆之礼。不得与 崔妃并举。似缘草创之初。人文未备。而四百年来。明良继兴。遗文坠典。无不焕然毕张。而独此一事。尚未有举。以为言者并与璿源谱牒。阙而不载。昭代觖典。恐无大于此矣。
国朝 陵寝祭享之用素膳。由于黄翼成力请。至今遵行。议者或以为踵前朝僧斋而然。或以为虑后日经费而然。愚意翼成虽非儒者。何至率百官庭请。为佞佛袭陋计耶。以为虑经费者。似得之矣。然考 国初礼制。 陵寝有朔望祭。 原庙有日三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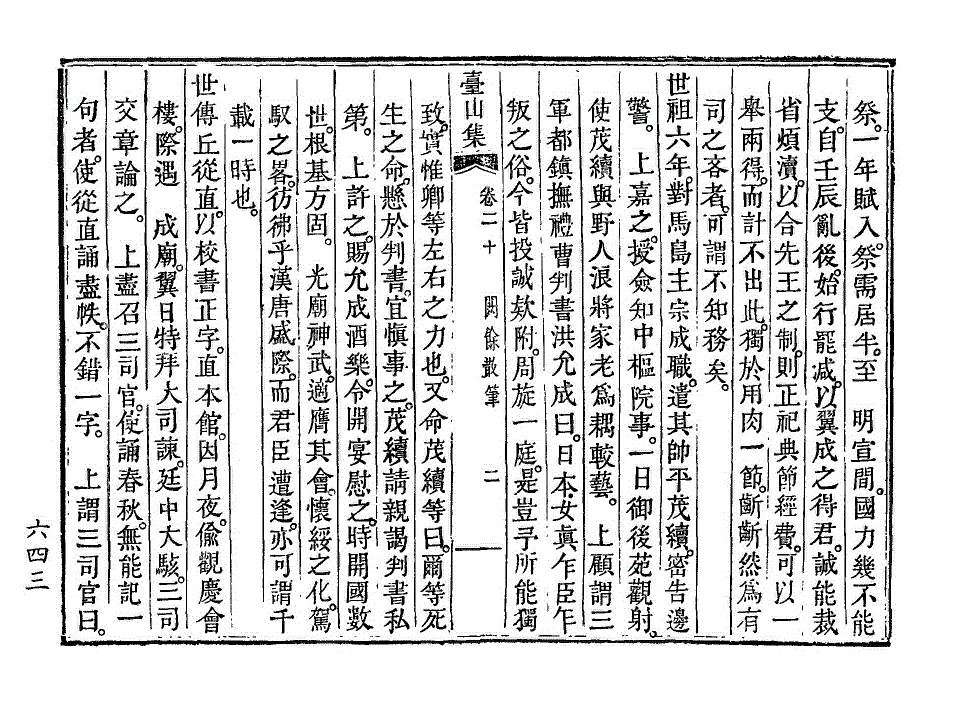 祭。一年赋入。祭需居半。至 明宣间。国力几不能支。自壬辰乱后。始行罢减。以翼成之得君。诚能裁省烦渎。以合先王之制。则正祀典节经费。可以一举两得。而计不出此。独于用肉一节。龂龂然为有司之吝者。可谓不知务矣。
祭。一年赋入。祭需居半。至 明宣间。国力几不能支。自壬辰乱后。始行罢减。以翼成之得君。诚能裁省烦渎。以合先王之制。则正祀典节经费。可以一举两得。而计不出此。独于用肉一节。龂龂然为有司之吝者。可谓不知务矣。世祖六年。对马岛主宗成职。遣其帅平茂续。密告边警。 上嘉之。授佥知中枢院事。一日御后苑观射。使茂续与野人浪将家老为耦较艺。 上顾谓三军都镇抚礼曹判书洪允成曰。日本,女真乍臣乍叛之俗。今皆投诚款附。周旋一庭。是岂予所能独致。实惟卿等左右之力也。又命茂续等曰。尔等死生之命。悬于判书。宜慎事之。茂续请亲谒判书私第。 上许之。赐允成酒乐。令开宴慰之。时开国数世。根基方固。 光庙神武。适膺其会。怀绥之化。驾驭之略。彷佛乎汉唐盛际。而君臣遭逢。亦可谓千载一时也。
世传丘从直。以校书正字。直本馆。因月夜。偷观庆会楼。际遇 成庙。翼日特拜大司谏。廷中大骇。三司交章论之。 上尽召三司官。使诵春秋。无能记一句者。使从直诵尽帙。不错一字。 上谓三司官曰。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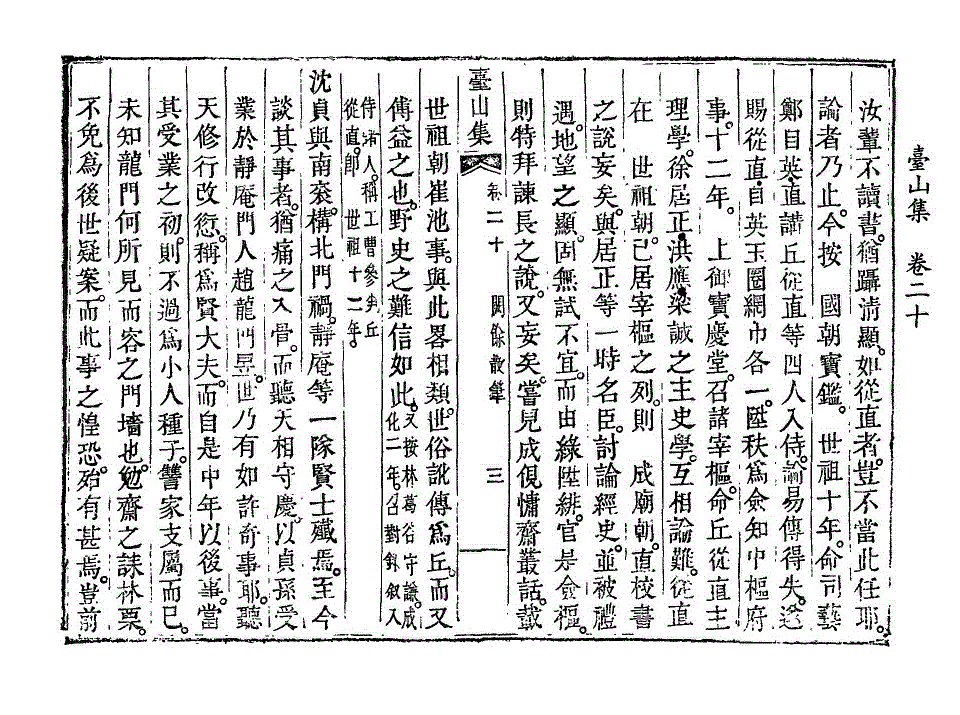 汝辈不读书。犹蹑清显。如从直者。岂不当此任耶。论者乃止。今按 国朝宝鉴。 世祖十年。命司艺郑自英,直讲丘从直等四人入侍。论易传得失。遂赐从直,自英玉圈网,巾各一。升秩为佥知中枢府事。十二年。 上御宝庆堂。召诸宰枢。命丘从直主理学。徐居正,洪应,梁诚之主史学。互相论难。从直在 世祖朝。已居宰枢之列。则 成庙朝。直校书之说妄矣。与居正等一时名臣。讨论经史。并被礼遇。地望之显。固无试不宜。而由绿升绯。官是佥枢。则特拜谏长之说。又妄矣。尝儿成伣慵斋丛话。载世祖朝崔池事。与此略相类。世俗讹传为丘。而又傅益之也。野史之难信如此。(又按林葛谷守谦。成化二年。召对录叙入侍诸人。称工曹参判丘从直。即 世祖十二年。)
汝辈不读书。犹蹑清显。如从直者。岂不当此任耶。论者乃止。今按 国朝宝鉴。 世祖十年。命司艺郑自英,直讲丘从直等四人入侍。论易传得失。遂赐从直,自英玉圈网,巾各一。升秩为佥知中枢府事。十二年。 上御宝庆堂。召诸宰枢。命丘从直主理学。徐居正,洪应,梁诚之主史学。互相论难。从直在 世祖朝。已居宰枢之列。则 成庙朝。直校书之说妄矣。与居正等一时名臣。讨论经史。并被礼遇。地望之显。固无试不宜。而由绿升绯。官是佥枢。则特拜谏长之说。又妄矣。尝儿成伣慵斋丛话。载世祖朝崔池事。与此略相类。世俗讹传为丘。而又傅益之也。野史之难信如此。(又按林葛谷守谦。成化二年。召对录叙入侍诸人。称工曹参判丘从直。即 世祖十二年。)沈贞与南衮。构北门祸。静庵等一队贤士歼焉。至今谈其事者。犹痛之入骨。而听天相守庆。以贞孙受业于静庵门人赵龙门昱。世乃有如许奇事耶。听天修行改愆。称为贤大夫。而自是中年以后事。当其受业之初。则不过为小人种子。雠家支属而已。未知龙门何所见而容之门墙也。勉斋之诔林栗。不免为后世疑案。而此事之惶恐。殆有甚焉。岂前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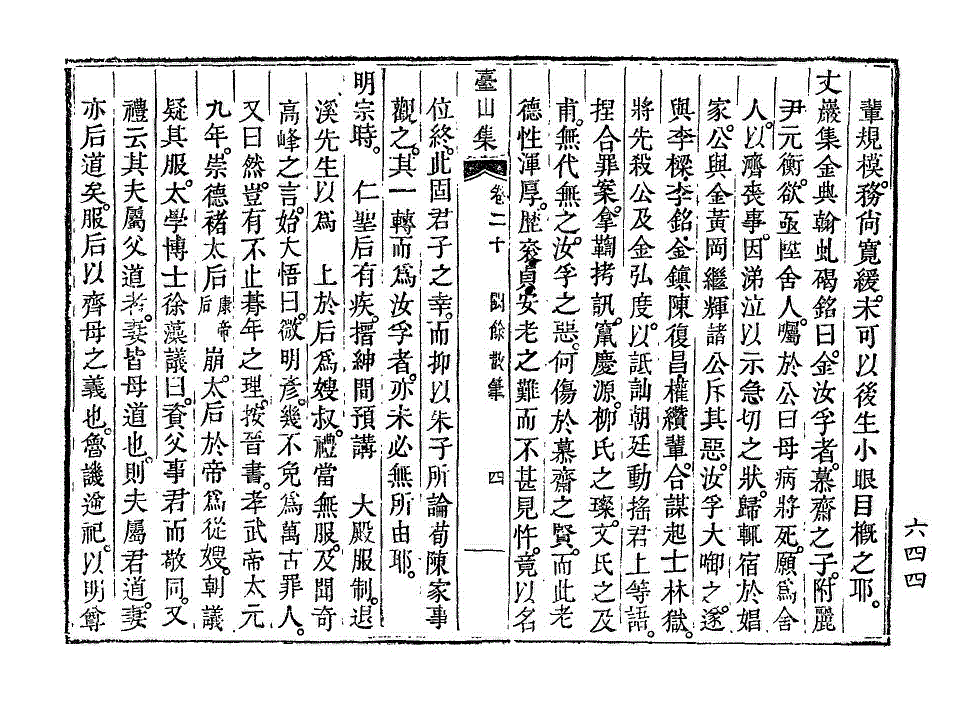 辈规模。务尚宽缓。未可以后生小眼目概之耶。
辈规模。务尚宽缓。未可以后生小眼目概之耶。丈岩集金典翰虬碣铭曰。金汝孚者。慕斋之子。附丽尹元衡。欲亟升舍人。嘱于公曰母病将死。愿为舍人。以济丧事。因涕泣以示急切之状。归辄宿于娼家。公与金黄冈继辉诸公斥其恶。汝孚大衔之。遂与李梁,李铭,金镇,陈复昌,权缵辈。合谋起士林狱。将先杀公及金弘度。以诋讪朝廷动摇君上等语。捏合罪案。拿鞫拷讯。窜庆源。柳氏之璨。文氏之及甫。无代无之。汝孚之恶。何伤于慕斋之贤。而此老德性浑厚。历衮,贞,安老之难而不甚见忤。竟以名位终。此固君子之幸。而抑以朱子所论荀陈家事观之。其一转而为汝孚者。亦未必无所由耶。
明宗时。 仁圣后有疾。搢绅间预讲 大殿服制。退溪先生以为 上于后为嫂叔。礼当无服。及闻奇高峰之言。始大悟曰。微明彦。几不免为万古罪人。又曰然。岂有不止期年之理。按晋书。孝武帝太元九年。崇德褚太后(康帝后)崩。太后于帝为从嫂。朝议疑其服。太学博士徐藻议曰。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云其夫属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齐母之义也。鲁讥逆祀。以明尊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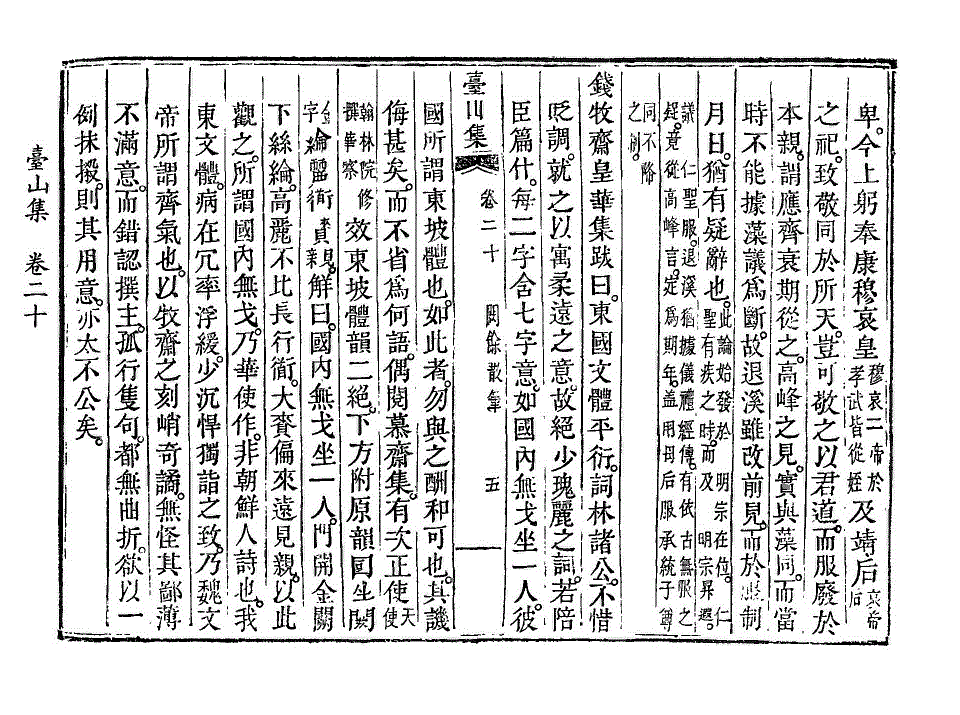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穆哀二帝于孝武皆从侄)及靖后(哀帝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齐衰期从之。高峰之见。实与藻同。而当时不能据藻议为断。故退溪虽改前见。而于服制月日。犹有疑辞也。(此论始发于 明宗在位。 仁圣有疾之时而及 明宗升遐。议 仁圣服。退溪犹据仪礼经传。有依古无服之疑。竟从高峰言。定为期年。盖用母后服承统子尊同不降之制。)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穆哀二帝于孝武皆从侄)及靖后(哀帝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齐衰期从之。高峰之见。实与藻同。而当时不能据藻议为断。故退溪虽改前见。而于服制月日。犹有疑辞也。(此论始发于 明宗在位。 仁圣有疾之时而及 明宗升遐。议 仁圣服。退溪犹据仪礼经传。有依古无服之疑。竟从高峰言。定为期年。盖用母后服承统子尊同不降之制。)钱牧斋皇华集跋曰。东国文体平衍。词林诸公。不惜贬调。就之以寓柔远之意。故绝少瑰丽之词。若陪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国内无戈坐一人。彼国所谓东坡体也。如此者。勿与之酬和可也。其讥侮甚矣。而不省为何语。偶阅慕斋集。有次正使(天使翰林院修撰华察)效东坡体韵二绝。下方附原韵国坐阙(金字)纶丽道赉亲解曰。国内无戈坐一人。门开金阙下丝纶。高丽不比长行道。大赉偏来远见亲。以此观之。所谓国内无戈。乃华使作。非朝鲜人诗也。我东文体。病在冗率浮缓。少沉悍独诣之致。乃魏文帝所谓齐气也。以牧斋之刻峭奇谲。无怪其鄙薄不满意。而错认撰主。孤行只句。都无曲折。欲以一例抹摋。则其用意。亦太不公矣。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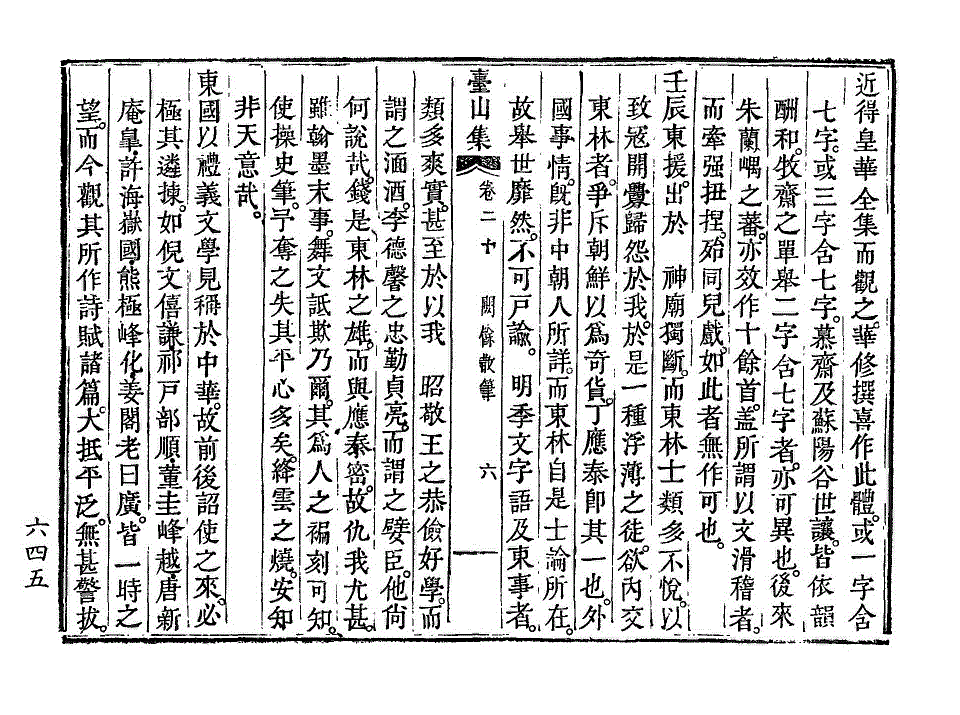 近得皇华全集而观之。华修撰喜作此体。或一字含七字。或三字含七字。慕斋及苏阳谷世让。皆依韵酬和。牧斋之单举二字含七字者。亦可异也。后来朱兰嵎之蕃。亦效作十馀首。盖所谓以文滑稽者。而牵强扭捏。殆同儿戏。如此者无作可也。
近得皇华全集而观之。华修撰喜作此体。或一字含七字。或三字含七字。慕斋及苏阳谷世让。皆依韵酬和。牧斋之单举二字含七字者。亦可异也。后来朱兰嵎之蕃。亦效作十馀首。盖所谓以文滑稽者。而牵强扭捏。殆同儿戏。如此者无作可也。壬辰东援。出于 神庙独断。而东林士类多不悦。以致寇开衅归怨于我。于是一种浮薄之徒。欲内交东林者。争斥朝鲜以为奇货。丁应泰即其一也。外国事情。既非中朝人所详。而东林自是士论所在。故举世靡然。不可户谕。 明季文字语及东事者。类多爽实。甚至于以我 昭敬王之恭俭好学。而谓之湎酒。李德馨之忠勤贞亮。而谓之嬖臣。他尚何说哉。钱是东林之雄。而与应泰密。故仇我尤甚。虽翰墨末事。舞文诋欺乃尔。其为人之褊刻可知。使操史笔。予夺之失其平心多矣。绛云之烧。安知非天意哉。
东国以礼义文学见称于中华。故前后诏使之来。必极其遴拣。如倪文僖谦,祁户部顺,董圭峰越,唐新庵皋,许海岳国,熊极峰化,姜阁老曰广。皆一时之望。而今观其所作诗赋诸篇。大抵平泛。无甚警拔。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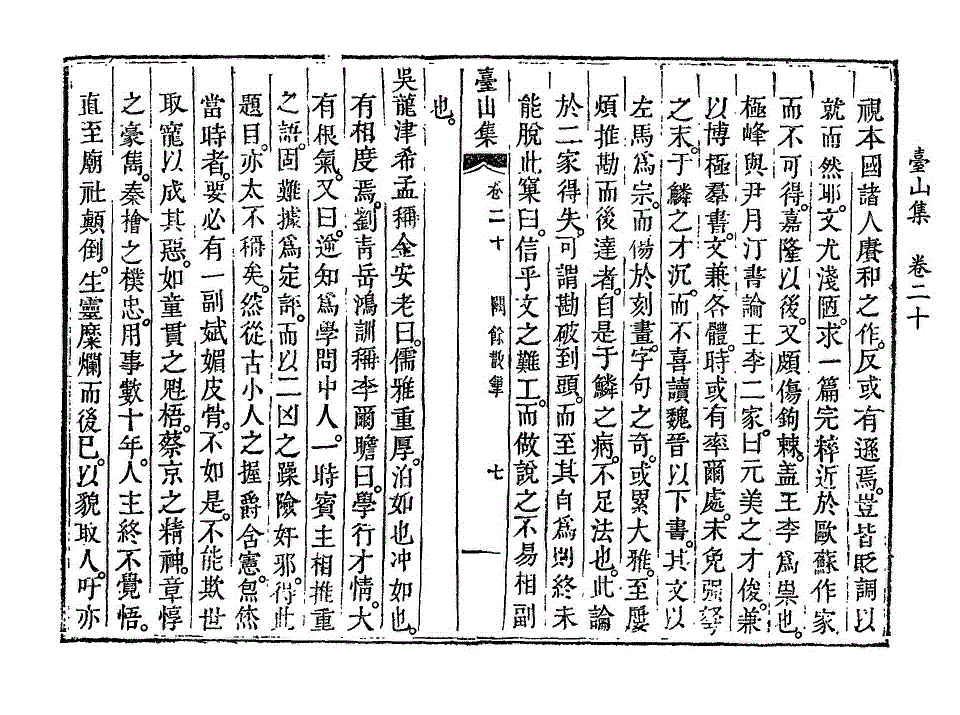 视本国诸人赓和之作。反或有逊焉。岂皆贬调以就而然耶。文尤浅陋。求一篇完粹近于欧苏作家而不可得。嘉隆以后。又颇伤钩棘。盖王李为崇也。极峰与尹月汀书论王李二家。曰元美之才俊。兼以博极群书。文兼各体。时或有率尔处。未免强弩之末。于鳞之才沉。而不喜读魏晋以下书。其文以左马为宗。而伤于刻画。字句之奇。或累大雅。至屡烦推勘而后达者。自是于鳞之病。不足法也。此论于二家得失。可谓勘破到头。而至其自为则终未能脱此窠臼。信乎文之难工。而做说之不易相副也。
视本国诸人赓和之作。反或有逊焉。岂皆贬调以就而然耶。文尤浅陋。求一篇完粹近于欧苏作家而不可得。嘉隆以后。又颇伤钩棘。盖王李为崇也。极峰与尹月汀书论王李二家。曰元美之才俊。兼以博极群书。文兼各体。时或有率尔处。未免强弩之末。于鳞之才沉。而不喜读魏晋以下书。其文以左马为宗。而伤于刻画。字句之奇。或累大雅。至屡烦推勘而后达者。自是于鳞之病。不足法也。此论于二家得失。可谓勘破到头。而至其自为则终未能脱此窠臼。信乎文之难工。而做说之不易相副也。吴龙津希孟称金安老曰。儒雅重厚。泊如也冲如也。有相度焉。刘青岳鸿训称李尔瞻曰。学行才情。大有根气。又曰。逆知为学问中人。一时宾主相推重之语。固难据为定评。而以二凶之躁险奸邪。得此题目。亦太不称矣。然从古小人之握爵含宪。炰炰当时者。要必有一副妩媚皮骨。不如是。不能欺世取宠以成其恶。如童贯之魁梧。蔡京之精神。章惇之豪隽。秦桧之朴忠。用事数十年。人主终不觉悟。直至庙社颠倒。生灵糜烂而后已。以貌取人。吁亦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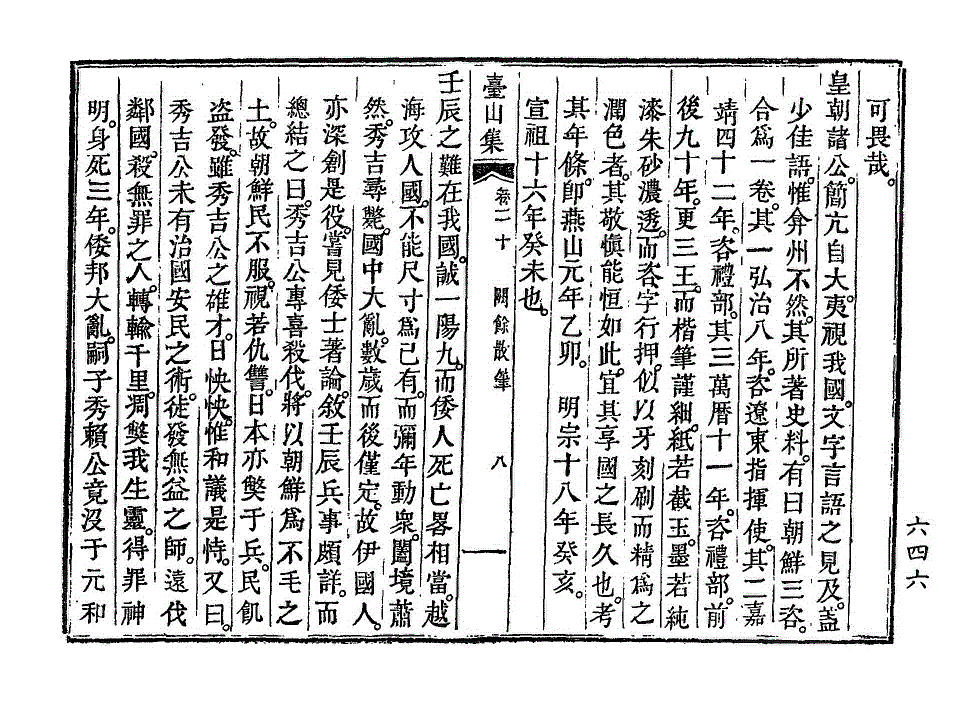 可畏哉。
可畏哉。皇朝诸公。简亢自大。夷视我国。文字言语之见及。盖少佳语。惟弇州不然。其所著史料。有曰朝鲜三咨。合为一卷。其一弘治八年。咨辽东指挥使。其二嘉靖四十二年。咨礼部。其三万历十一年。咨礼部。前后九十年。更三王。而楷笔谨细。纸若截玉。墨若纯漆朱砂浓透。而咨字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为之润色者。其敬慎能恒如此。宜其享国之长久也。考其年条。即燕山元年乙卯。 明宗十八年癸亥。 宣祖十六年癸未也。
壬辰之难在我国。诚一阳九。而倭人死亡略相当。越海攻人国。不能尺寸为己有。而弥年动众。阖境萧然。秀吉寻毙。国中大乱。数岁而后仅定。故伊国人。亦深创是役。尝见倭士著论。叙壬辰兵事颇详。而总结之曰。秀吉公专喜杀伐。将以朝鲜为不毛之土。故朝鲜民不服。视若仇雠。日本亦弊于兵。民饥盗发。虽秀吉公之雄才。日怏怏。惟和议是恃。又曰。秀吉公未有治国安民之术。徒发无益之师。远伐邻国。杀无罪之人。转输千里。凋弊我生灵。得罪神明。身死三年。倭邦大乱。嗣子秀赖公竟没于元和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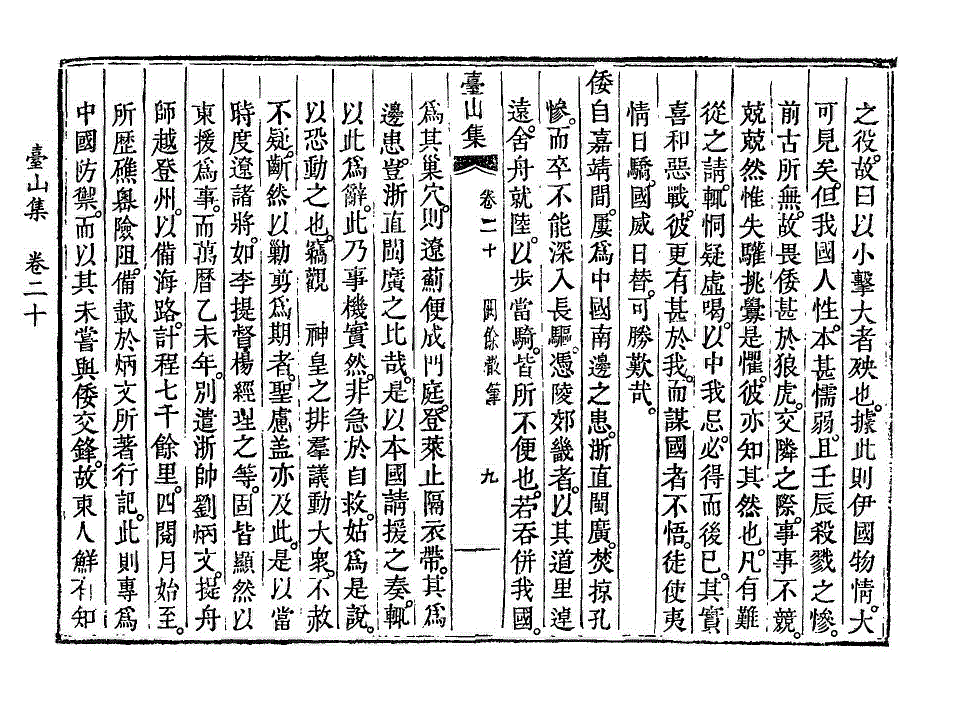 之役。故曰以小击大者殃也。据此则伊国物情。大可见矣。但我国人性。本甚懦弱。且壬辰杀戮之惨。前古所无。故畏倭甚于狼虎。交邻之际。事事不竞。兢兢然惟失驩挑衅是惧。彼亦知其然也。凡有难从之请。辄恫疑虚喝。以中我忌。必得而后已。其实喜和恶战。彼更有甚于我。而谋国者不悟。徒使夷情日骄。国威日替。可胜叹哉。
之役。故曰以小击大者殃也。据此则伊国物情。大可见矣。但我国人性。本甚懦弱。且壬辰杀戮之惨。前古所无。故畏倭甚于狼虎。交邻之际。事事不竞。兢兢然惟失驩挑衅是惧。彼亦知其然也。凡有难从之请。辄恫疑虚喝。以中我忌。必得而后已。其实喜和恶战。彼更有甚于我。而谋国者不悟。徒使夷情日骄。国威日替。可胜叹哉。倭自嘉靖间。屡为中国南边之患。浙直闽广。焚掠孔惨。而卒不能深入长驱。凭陵郊畿者。以其道里逴远。舍舟就陆。以步当骑。皆所不便也。若吞并我国。为其巢穴。则辽蓟便成门庭。登莱止隔衣带。其为边患。岂浙直闽广之比哉。是以本国请援之奏。辄以此为辞。此乃事机实然。非急于自救。姑为是说。以恐动之也。窃观 神皇之排群议动大众。不赦不疑。龂然以剿剪为期者。圣虑盖亦及此。是以当时度辽诸将。如李提督,杨经理之等。固皆显然以东援为事。而万历乙未年。别遣浙帅刘炳文。提舟师越登州。以备海路。计程七千馀里。四阅月始至。所历礁岙险阻。备载于炳文所著行记。此则专为中国防御。而以其未尝与倭交锋。故东人鲜有知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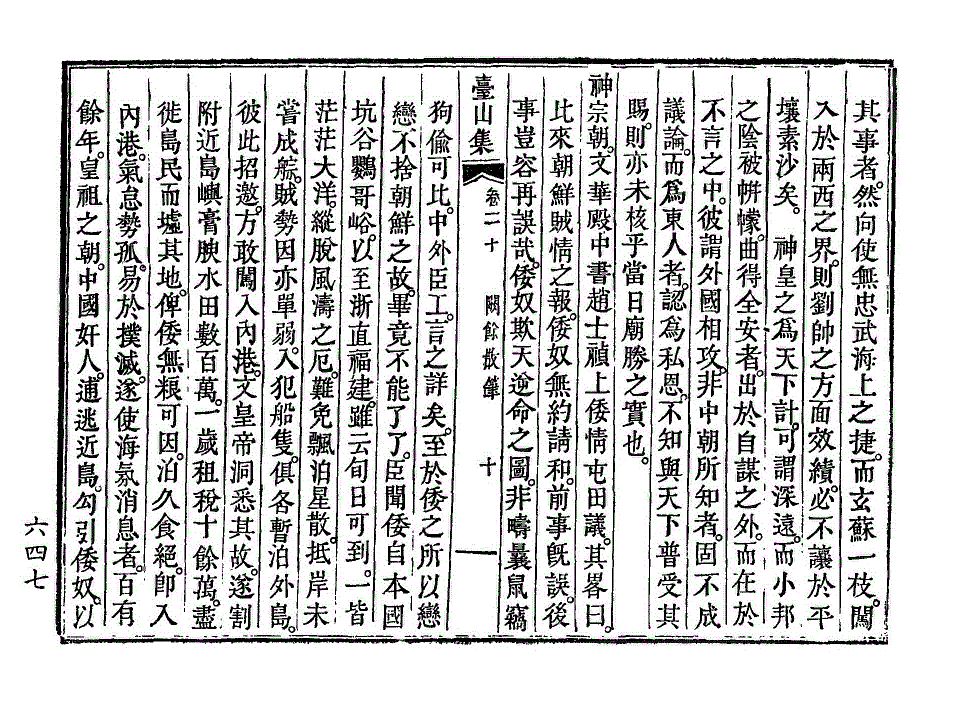 其事者。然向使无忠武海上之捷。而玄苏一枝。闯入于两西之界。则刘帅之方面效绩。必不让于平壤素沙矣。 神皇之为天下计。可谓深远。而小邦之阴被帲幪。曲得全安者。出于自谋之外。而在于不言之中。彼谓外国相攻。非中朝所知者。固不成议论。而为东人者。认为私恩。不知与天下普受其赐。则亦未核乎当日庙胜之实也。
其事者。然向使无忠武海上之捷。而玄苏一枝。闯入于两西之界。则刘帅之方面效绩。必不让于平壤素沙矣。 神皇之为天下计。可谓深远。而小邦之阴被帲幪。曲得全安者。出于自谋之外。而在于不言之中。彼谓外国相攻。非中朝所知者。固不成议论。而为东人者。认为私恩。不知与天下普受其赐。则亦未核乎当日庙胜之实也。神宗朝。文华殿中书赵士祯上倭情屯田议。其略曰。比来朝鲜贼情之报。倭奴无约请和。前事既误。后事岂容再误哉。倭奴欺天逆命之图。非畴曩鼠窃狗偷可比。中外臣工。言之详矣。至于倭之所以恋恋不舍朝鲜之故。毕竟不能了了。臣闻倭自本国坑谷鹦哥峪。以至浙直福建。虽云旬日可到。一皆茫茫大洋。纵脱风涛之厄。难免飘泊星散。抵岸未尝成䑸。贼势因亦单弱。入犯船只。俱各暂泊外岛。彼此招邀。方敢闯入内港。文皇帝洞悉其故。遂割附近岛屿膏腴水田数百万。一岁租税十馀万。尽徙岛民而墟其地。俾倭无粮可因。泊久食绝。即入内港。气怠势孤。易于扑灭。遂使海氛消息者。百有馀年。皇祖之朝。中国奸人。逋逃近岛。勾引倭奴。以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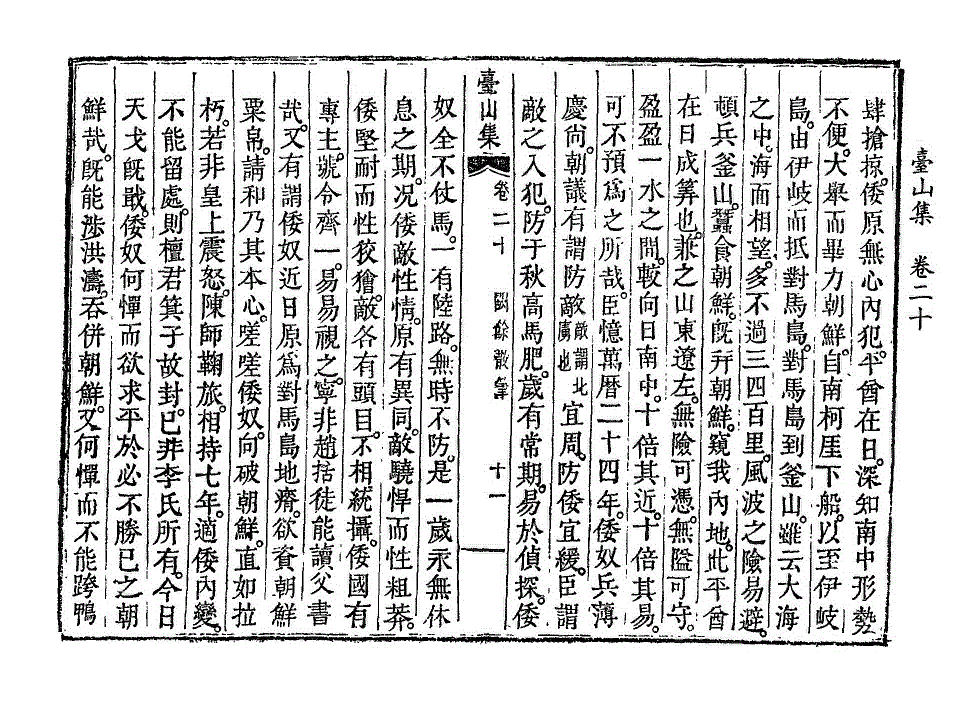 肆抢掠。倭原无心内犯。平酋在日。深知南中形势不便。大举而毕力朝鲜。自南柯厓下船。以至伊岐岛。由伊岐而抵对马岛。对马岛到釜山。虽云大海之中。海而相望。多不过三四百里。风波之险易避。顿兵釜山。蚕食朝鲜。既并朝鲜。窥我内地。此平酋在日成算也。兼之山东辽左。无险可凭。无隘可守。盈盈一水之间。较向日南中。十倍其近。十倍其易。可不预为之所哉。臣忆万历二十四年。倭奴兵薄庆尚。朝议有谓防敌(敌谓北虏也)宜周。防倭宜缓。臣谓敌之入犯。防于秋高马肥。岁有常期。易于侦探。倭奴全不仗马。一有陆路。无时不防。是一岁永无休息之期。况倭敌性情。原有异同。敌骁悍而性粗莽。倭坚耐而性狡狯。敌各有头目。不相统摄。倭国有专主。号令齐一。易易视之。宁非赵括徒能读父书哉。又有谓倭奴近日原为对马岛地瘠。欲资朝鲜粟帛。请和乃其本心。嗟嗟倭奴。向破朝鲜。直如拉朽。若非皇上震怒。陈师鞠旅。相持七年。适倭内变。不能留处。则檀君箕子故封。已非李氏所有。今日天戈既戢。倭奴何惮而欲求平于必不胜己之朝鲜哉。既能涉洪涛。吞并朝鲜。又何惮而不能跨鸭
肆抢掠。倭原无心内犯。平酋在日。深知南中形势不便。大举而毕力朝鲜。自南柯厓下船。以至伊岐岛。由伊岐而抵对马岛。对马岛到釜山。虽云大海之中。海而相望。多不过三四百里。风波之险易避。顿兵釜山。蚕食朝鲜。既并朝鲜。窥我内地。此平酋在日成算也。兼之山东辽左。无险可凭。无隘可守。盈盈一水之间。较向日南中。十倍其近。十倍其易。可不预为之所哉。臣忆万历二十四年。倭奴兵薄庆尚。朝议有谓防敌(敌谓北虏也)宜周。防倭宜缓。臣谓敌之入犯。防于秋高马肥。岁有常期。易于侦探。倭奴全不仗马。一有陆路。无时不防。是一岁永无休息之期。况倭敌性情。原有异同。敌骁悍而性粗莽。倭坚耐而性狡狯。敌各有头目。不相统摄。倭国有专主。号令齐一。易易视之。宁非赵括徒能读父书哉。又有谓倭奴近日原为对马岛地瘠。欲资朝鲜粟帛。请和乃其本心。嗟嗟倭奴。向破朝鲜。直如拉朽。若非皇上震怒。陈师鞠旅。相持七年。适倭内变。不能留处。则檀君箕子故封。已非李氏所有。今日天戈既戢。倭奴何惮而欲求平于必不胜己之朝鲜哉。既能涉洪涛。吞并朝鲜。又何惮而不能跨鸭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8L 页
 绿衣带之水。窥兵内地哉。仍请屯田辽左。为持久制胜之计。此议似在己亥后日本请和之时。所论倭情。凿凿中窾。而其称朝议二段。即当时东林一队之论也。赵是嘉靖间人。逮事 神宗。年已老矣。而出位论事。恳恳如此。可谓一代奇士。又尝著备边车铳议。捐赀制造。并图式进呈。而未见采施。
绿衣带之水。窥兵内地哉。仍请屯田辽左。为持久制胜之计。此议似在己亥后日本请和之时。所论倭情。凿凿中窾。而其称朝议二段。即当时东林一队之论也。赵是嘉靖间人。逮事 神宗。年已老矣。而出位论事。恳恳如此。可谓一代奇士。又尝著备边车铳议。捐赀制造。并图式进呈。而未见采施。汉阴李公德馨。当光海初为首相。上劄数千言。极论新政。有曰进言亦有所宜。如先朝之失政。尽言于大行大王之时则为可矣。到今言之。是不忠也。谋危请封。发言于郑仁弘远窜之日则为可矣。到今言之。是希望也。处事幽闇。自附效忠。则是利身而贼君也。请罪权臣。出于相识。则是前附而后卖也。凡士之患得患失者。惟以好官爵为念。懵学蔑识者。惟以随时论为是。不计事体。不顾廉耻。不择是非。权势所在。褰裳争赴。攘臂为功。朝廷之累。因此多矣。深恐日后又有以杀戮导殿下者。伏愿深省焉。又引程传干蛊之说。请尽孝母后。真蓍龟药石之言也。光海十五年。许多败證。莫不权舆于此。向使少加谛听。行得一半。则何至有癸亥三月之事耶。与李子常书曰。以岭外帅臣自处。而若超然于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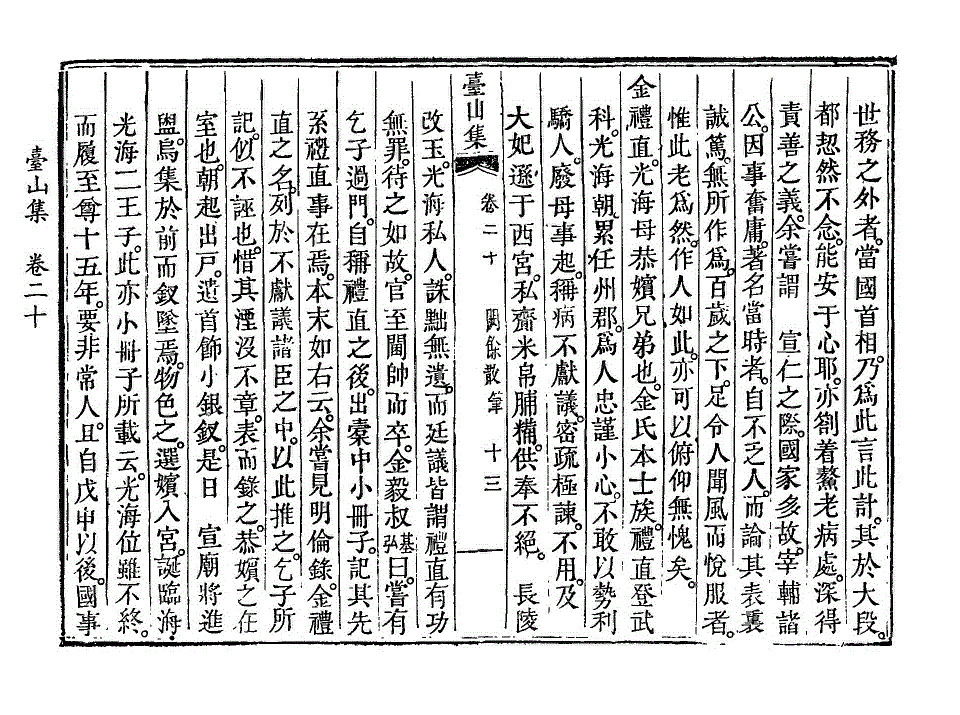 世务之外者。当国首相。乃为此言此计。其于大段。都恝然不念。能安于心耶。亦劄着鳌老病处。深得责善之义。余尝谓 宣仁之际。国家多故。宰辅诸公。因事奋庸。著名当时者。自不乏人。而论其表里诚笃。无所作为。百岁之下。足令人闻风而悦服者。惟此老为然。作人如此。亦可以俯仰无愧矣。
世务之外者。当国首相。乃为此言此计。其于大段。都恝然不念。能安于心耶。亦劄着鳌老病处。深得责善之义。余尝谓 宣仁之际。国家多故。宰辅诸公。因事奋庸。著名当时者。自不乏人。而论其表里诚笃。无所作为。百岁之下。足令人闻风而悦服者。惟此老为然。作人如此。亦可以俯仰无愧矣。金礼直。光海母恭嫔兄弟也。金氏本士族。礼直登武科。光海朝累任州郡。为人忠谨小心。不敢以势利骄人。废母事起。称病不献议。密疏极谏。不用。及 大妃逊于西宫。私赍米帛脯糒。供奉不绝。 长陵改玉。光海私人。诛黜无遗。而廷议皆谓礼直有功无罪。待之如故。官至阃帅而卒。金毅叔(基弘)曰。尝有乞子过门。自称礼直之后。出橐中小册子。记其先系礼直事在焉。本末如右云。余尝见明伦录。金礼直之名。列于不献议诸臣之中。以此推之。乞子所记。似不诬也。惜其湮没不章。表而录之。恭嫔之在室也。朝起出户。遗首饰小银钗。是日 宣庙将进盥。乌集于前而钗坠焉。物色之。选嫔入宫。诞临海,光海二王子。此亦小册子所载云。光海位虽不终。而履至尊十五年。要非常人。且自戊申以后。国事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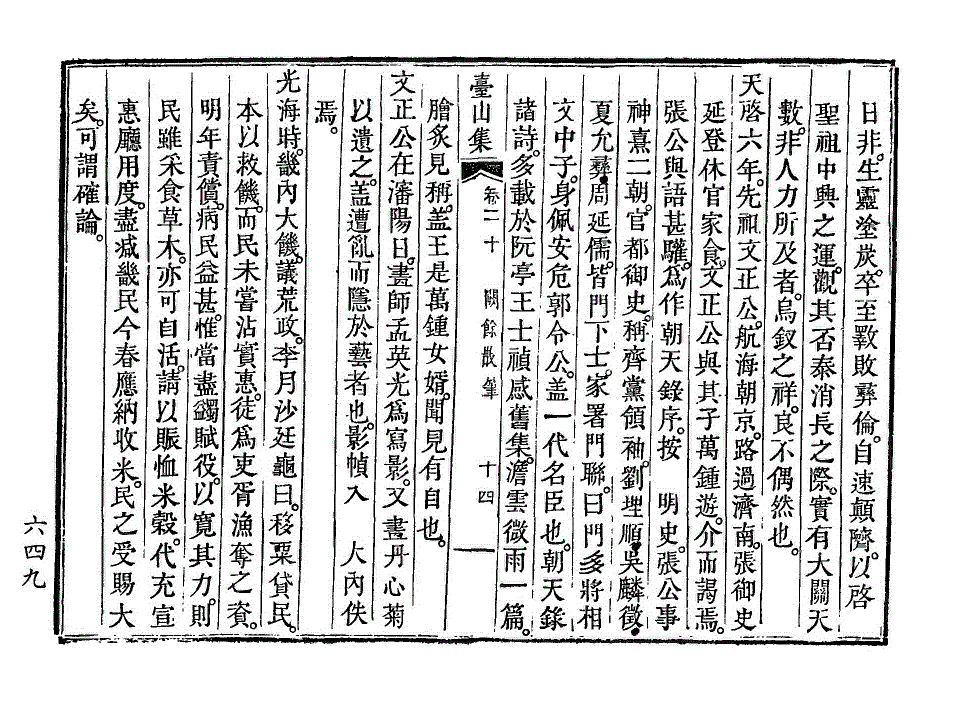 日非。生灵涂炭。卒至斁败彝伦。自速颠隮。以启 圣祖中兴之运。观其否泰消长之际。实有大关天数。非人力所及者。乌钗之祥。良不偶然也。
日非。生灵涂炭。卒至斁败彝伦。自速颠隮。以启 圣祖中兴之运。观其否泰消长之际。实有大关天数。非人力所及者。乌钗之祥。良不偶然也。天启六年。先祖文正公。航海朝京。路过济南。张御史延登休官家食。文正公与其子万钟游。介而谒焉。张公与语甚驩。为作朝天录序。按 明史。张公事神熹二朝。官都御史。称齐党领补。刘理顺,吴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门下士。家署门联。曰门多将相文中子。身佩安危郭令公。盖一代名臣也。朝天录诸诗。多载于阮亭王士祯感旧集。澹云微雨一篇。脍炙见称。盖王是万钟女婿。闻见有自也。
文正公在沈阳日。画师孟英光为写影。又画丹心菊以遗之。盖遭乱而隐于艺者也。影帧入 大内佚焉。
光海时。畿内大饥。议荒政。李月沙廷龟曰。移粟贷民。本以救饥。而民未尝沾实惠。徒为吏胥渔夺之资。明年责偿。病民益甚。惟当尽蠲赋役。以宽其力。则民虽采食草木。亦可自活。请以赈恤米谷。代充宣惠厅用度。尽减畿民今春应纳收米。民之受赐大矣。可谓确论。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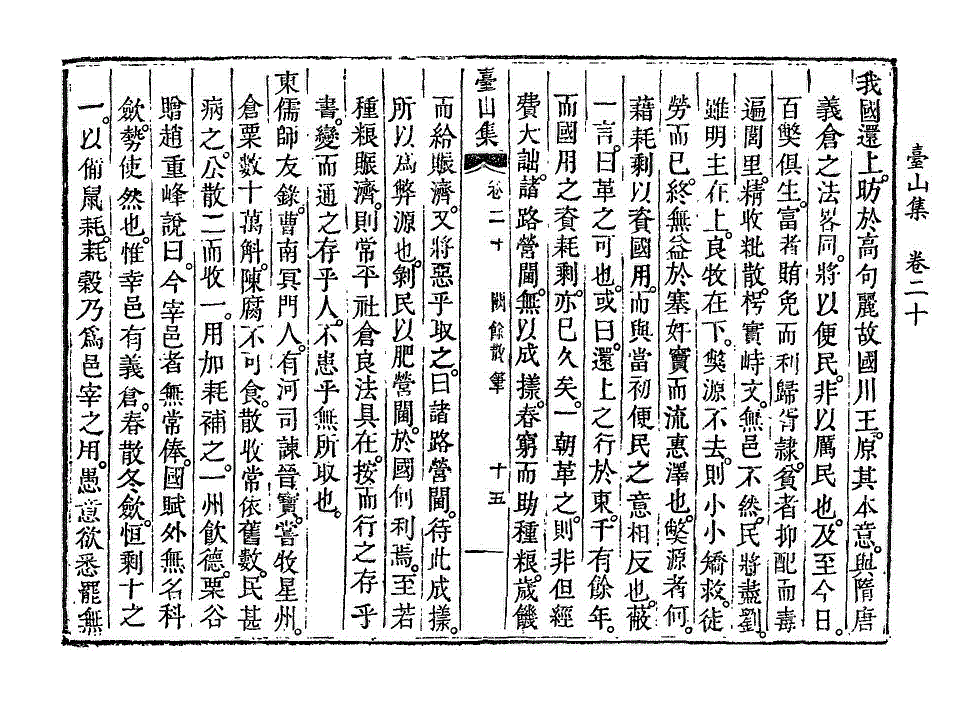 我国还上。昉于高句丽故国川王。原其本意。与隋唐义仓之法略同。将以便民。非以厉民也。及至今日。百弊俱生。富者贿免而利归胥隶。贫者抑配而毒遍闾里。精收秕散。枵实峙文。无邑不然。民将尽刘。虽明主在上。良牧在下。弊源不去。则小小矫救。徒劳而已。终无益于塞奸窦而流惠泽也。弊源者何。藉耗剩以资国用。而与当初便民之意相反也。蔽一言。曰革之可也。或曰。还上之行于东。千有馀年。而国用之资耗剩。亦已久矣。一朝革之。则非但经费大诎。诸路营阃。无以成㨾。春穷而助种粮。岁饥而给赈济。又将恶乎取之。曰诸路营阃。待此成㨾。所以为弊源也。剥民以肥营阃。于国何利焉。至若种粮赈济。则常平社仓良法具在。按而行之存乎书。变而通之存乎人。不患乎无所取也。
我国还上。昉于高句丽故国川王。原其本意。与隋唐义仓之法略同。将以便民。非以厉民也。及至今日。百弊俱生。富者贿免而利归胥隶。贫者抑配而毒遍闾里。精收秕散。枵实峙文。无邑不然。民将尽刘。虽明主在上。良牧在下。弊源不去。则小小矫救。徒劳而已。终无益于塞奸窦而流惠泽也。弊源者何。藉耗剩以资国用。而与当初便民之意相反也。蔽一言。曰革之可也。或曰。还上之行于东。千有馀年。而国用之资耗剩。亦已久矣。一朝革之。则非但经费大诎。诸路营阃。无以成㨾。春穷而助种粮。岁饥而给赈济。又将恶乎取之。曰诸路营阃。待此成㨾。所以为弊源也。剥民以肥营阃。于国何利焉。至若种粮赈济。则常平社仓良法具在。按而行之存乎书。变而通之存乎人。不患乎无所取也。东儒师友录。曹南冥门人。有河司谏晋宝。尝牧星州。仓粟数十万斛。陈腐不可食。散收常依旧数。民甚病之。公散二而收一。用加耗补之。一州饮德。栗谷赠赵重峰说曰。今宰邑者无常俸。国赋外无名科敛。势使然也。惟幸邑有义仓。春散冬敛。恒剩十之一。以备鼠耗。耗谷乃为邑宰之用。愚意欲悉罢无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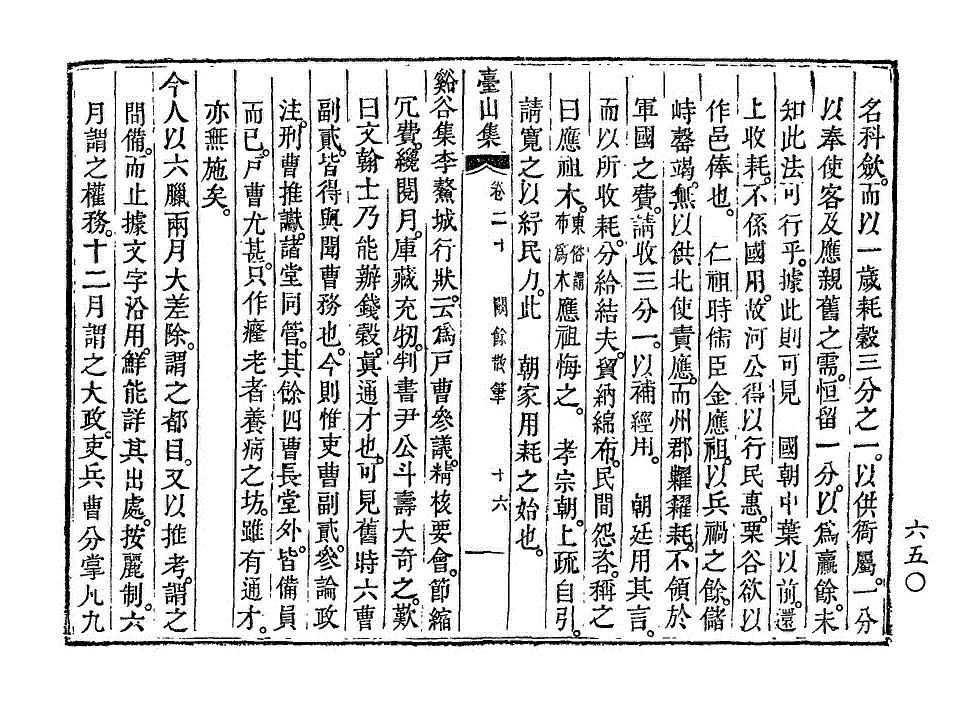 名科敛。而以一岁耗谷三分之一。以供衙属。一分以奉使客及应亲旧之需。恒留一分。以为赢馀。未知此法可行乎。据此则可见 国朝中叶以前。还上收耗。不系国用。故河公得以行民惠。栗谷欲以作邑俸也。 仁祖时儒臣金应祖。以兵祸之馀。储峙罄竭。无以供北使责应。而州郡粜籴耗。不领于军国之费。请收三分一。以补经用。 朝廷用其言。而以所收耗。分给结夫。贸纳绵布。民间怨咨。称之曰应祖木。(东俗谓布为木)应祖悔之。 孝宗朝。上疏自引。请宽之以纾民力。此 朝家用耗之始也。
名科敛。而以一岁耗谷三分之一。以供衙属。一分以奉使客及应亲旧之需。恒留一分。以为赢馀。未知此法可行乎。据此则可见 国朝中叶以前。还上收耗。不系国用。故河公得以行民惠。栗谷欲以作邑俸也。 仁祖时儒臣金应祖。以兵祸之馀。储峙罄竭。无以供北使责应。而州郡粜籴耗。不领于军国之费。请收三分一。以补经用。 朝廷用其言。而以所收耗。分给结夫。贸纳绵布。民间怨咨。称之曰应祖木。(东俗谓布为木)应祖悔之。 孝宗朝。上疏自引。请宽之以纾民力。此 朝家用耗之始也。溪谷集李鳌城行状。云为户曹参议。精核要会。节缩冗费。才阅月。库藏充牣。判书尹公斗寿大奇之。叹曰文翰士乃能办钱谷。真通才也。可见旧时六曹副贰。皆得与闻曹务也。今则惟吏曹副贰。参论政注。刑曹推谳。诸堂同管。其馀四曹长堂外。皆备员而已。户曹尤甚。只作癃老者养病之坊。虽有通才。亦无施矣。
今人以六腊两月大差除。谓之都目。又以推考。谓之问备。而止据文字沿用。鲜能详其出处。按丽制。六月谓之权务。十二月谓之大政。吏兵曹分掌凡九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1H 页
 品以上及府卫队正以上府史胥徒。皆著其年月。录其功过。每于岁杪升黜。谓之都目政。李益斋齐贤疏云置考功司。标其功过。论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则可以绝请谒之徒。杜侥倖之门。据此则并权务通谓之都目也。盖都目云者。乃标功过论才否之目录文字。即今之京外褒贬题目。而据此褒贬。以行黜陟。故名其政曰都目政。今直以注拟三望之列书者。认作都目。则失其旨矣。古者官师相规。而同事一君。有兄弟之谊。苟非大故。不宜遽彰其失于君前。故凡有差失。必以书牍私相问难。其言果是。则受之者缄答示屈。如或情有未悉。事在当暴。则亦备细辨明。以待归一。故谓之问备。虽于大官亦然。 明朝文集。有揭帖问难。即此意也。近来无此风。而所谓推考者。毛摘细故。直用举劾之例。陈于上前而请勘。不至于递罢。故冒称问备。而其实空言而已。未尝有问备之事也。其或自上特命推考。而令依爰辞例供对者。谓之缄辞推考。盖略仿故规。而亦与同朝责善之本意左矣。
品以上及府卫队正以上府史胥徒。皆著其年月。录其功过。每于岁杪升黜。谓之都目政。李益斋齐贤疏云置考功司。标其功过。论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则可以绝请谒之徒。杜侥倖之门。据此则并权务通谓之都目也。盖都目云者。乃标功过论才否之目录文字。即今之京外褒贬题目。而据此褒贬。以行黜陟。故名其政曰都目政。今直以注拟三望之列书者。认作都目。则失其旨矣。古者官师相规。而同事一君。有兄弟之谊。苟非大故。不宜遽彰其失于君前。故凡有差失。必以书牍私相问难。其言果是。则受之者缄答示屈。如或情有未悉。事在当暴。则亦备细辨明。以待归一。故谓之问备。虽于大官亦然。 明朝文集。有揭帖问难。即此意也。近来无此风。而所谓推考者。毛摘细故。直用举劾之例。陈于上前而请勘。不至于递罢。故冒称问备。而其实空言而已。未尝有问备之事也。其或自上特命推考。而令依爰辞例供对者。谓之缄辞推考。盖略仿故规。而亦与同朝责善之本意左矣。大丧公除前。大臣入直政院。禀决庶务。谓之院相。即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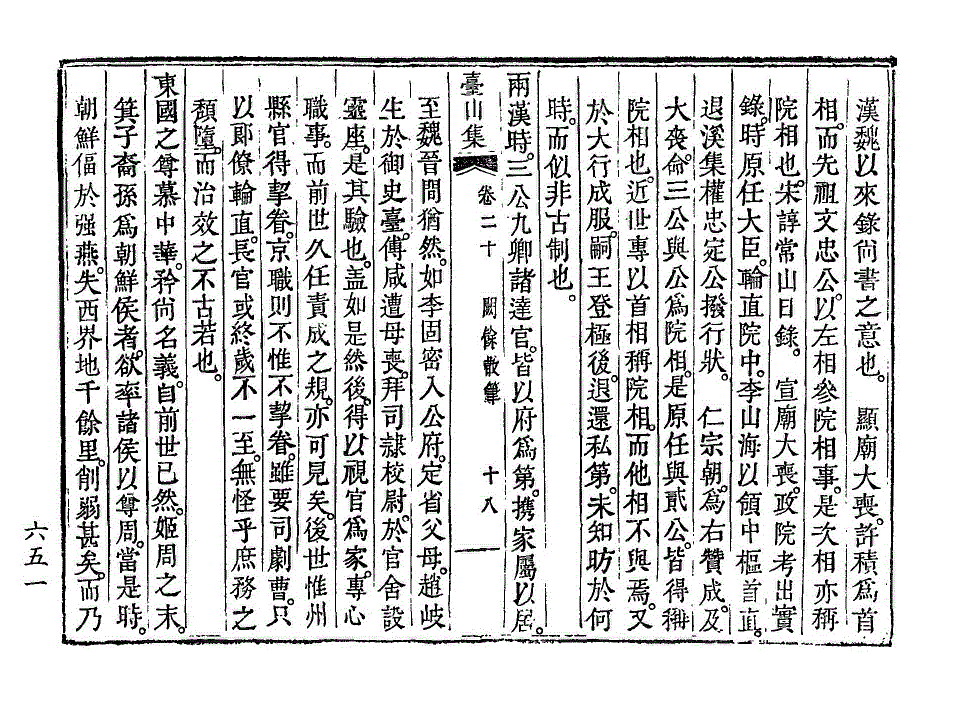 汉魏以来录尚书之意也。 显庙大丧。许积为首相。而先祖文忠公。以左相参院相事。是次相亦称院相也。宋谆常山日录。 宣庙大丧。政院考出实录。时原任大臣。轮直院中。李山海以领中枢首直。退溪集权忠定公橃行状。 仁宗朝。为右赞成。及大丧。命三公与公为院相。是原任与贰公。皆得称院相也。近世专以首相称院相。而他相不与焉。又于大行成服。嗣王登极后。退还私第。未知昉于何时。而似非古制也。
汉魏以来录尚书之意也。 显庙大丧。许积为首相。而先祖文忠公。以左相参院相事。是次相亦称院相也。宋谆常山日录。 宣庙大丧。政院考出实录。时原任大臣。轮直院中。李山海以领中枢首直。退溪集权忠定公橃行状。 仁宗朝。为右赞成。及大丧。命三公与公为院相。是原任与贰公。皆得称院相也。近世专以首相称院相。而他相不与焉。又于大行成服。嗣王登极后。退还私第。未知昉于何时。而似非古制也。两汉时。三公九卿诸达官。皆以府为第。携家属以居。至魏晋间犹然。如李固密入公府。定省父母。赵岐生于御史台。傅咸遭母丧。拜司隶校尉。于官舍设灵座。是其验也。盖如是然后。得以视官为家。专心职事。而前世久任责成之规。亦可见矣。后世惟州县官得挈眷。京职则不惟不挈眷。虽要司剧曹。只以郎僚轮直。长官或终岁不一至。无怪乎庶务之颓堕。而治效之不古若也。
东国之尊慕中华。矜尚名义。自前世已然。姬周之末。箕子裔孙为朝鲜侯者。欲率诸侯以尊周。当是时。朝鲜偪于强燕。失西界地千馀里。削弱甚矣。而乃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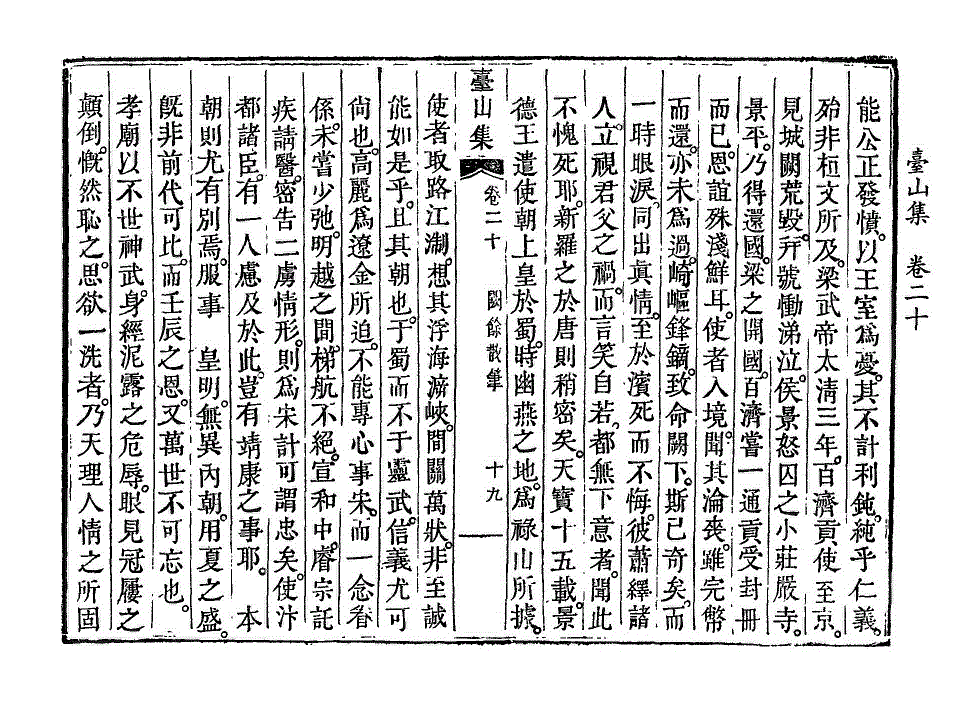 能公正发愤。以王室为忧。其不计利钝。纯乎仁义。殆非桓文所及。梁武帝太清三年。百济贡使至京。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之小庄严寺。景平。乃得还国。梁之开国。百济尝一通贡受封册而已。恩谊殊浅鲜耳。使者入境。闻其沦丧。虽完币而还。亦未为过。崎岖锋镝。致命阙下。斯已奇矣。而一时眼泪。同出真情。至于滨死而不悔。彼萧绎诸人。立视君父之祸。而言笑自若。都无下意者。闻此不愧死耶。新罗之于唐则稍密矣。天宝十五载。景德王遣使朝上皇于蜀。时幽燕之地。为禄山所据。使者取路江浙。想其浮海溯峡。间关万状。非至诚能如是乎。且其朝也。于蜀而不于灵武。信义尤可尚也。高丽为辽金所迫。不能专心事宋。而一念眷系。未尝少弛。明越之间。梯航不绝。宣和中。睿宗托疾请医。密告二虏情形。则为宋计可谓忠矣。使汴都诸臣。有一人虑及于此。岂有靖康之事耶。 本朝则尤有别焉。服事 皇明。无异内朝。用夏之盛。既非前代可比。而壬辰之恩。又万世不可忘也。 孝庙以不世神武。身经泥露之危辱。眼见冠屦之颠倒。慨然耻之。思欲一洗者。乃天理人情之所固
能公正发愤。以王室为忧。其不计利钝。纯乎仁义。殆非桓文所及。梁武帝太清三年。百济贡使至京。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之小庄严寺。景平。乃得还国。梁之开国。百济尝一通贡受封册而已。恩谊殊浅鲜耳。使者入境。闻其沦丧。虽完币而还。亦未为过。崎岖锋镝。致命阙下。斯已奇矣。而一时眼泪。同出真情。至于滨死而不悔。彼萧绎诸人。立视君父之祸。而言笑自若。都无下意者。闻此不愧死耶。新罗之于唐则稍密矣。天宝十五载。景德王遣使朝上皇于蜀。时幽燕之地。为禄山所据。使者取路江浙。想其浮海溯峡。间关万状。非至诚能如是乎。且其朝也。于蜀而不于灵武。信义尤可尚也。高丽为辽金所迫。不能专心事宋。而一念眷系。未尝少弛。明越之间。梯航不绝。宣和中。睿宗托疾请医。密告二虏情形。则为宋计可谓忠矣。使汴都诸臣。有一人虑及于此。岂有靖康之事耶。 本朝则尤有别焉。服事 皇明。无异内朝。用夏之盛。既非前代可比。而壬辰之恩。又万世不可忘也。 孝庙以不世神武。身经泥露之危辱。眼见冠屦之颠倒。慨然耻之。思欲一洗者。乃天理人情之所固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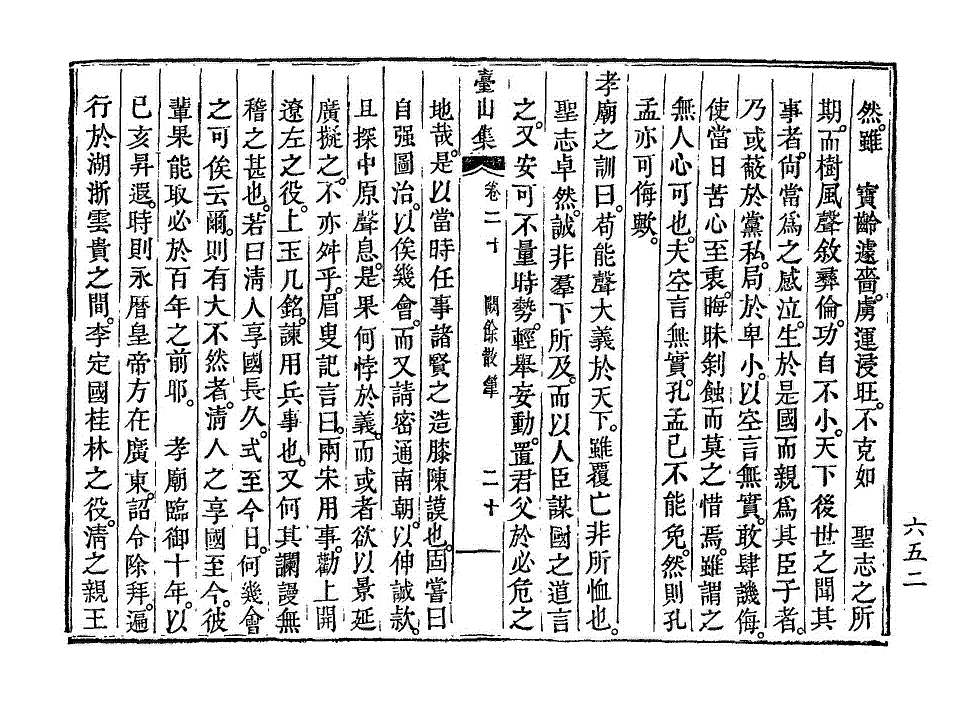 然。虽 宝龄遽啬。虏运浸旺。不克如 圣志之所期。而树风声叙彝伦。功自不小。天下后世之闻其事者。尚当为之感泣。生于是国而亲为其臣子者。乃或蔽于党私。局于卑小。以空言无实。敢肆讥侮。使当日苦心至衷。晦昧剥蚀而莫之惜焉。虽谓之无人心可也。夫空言无实。孔孟已不能免。然则孔孟亦可侮欤。
然。虽 宝龄遽啬。虏运浸旺。不克如 圣志之所期。而树风声叙彝伦。功自不小。天下后世之闻其事者。尚当为之感泣。生于是国而亲为其臣子者。乃或蔽于党私。局于卑小。以空言无实。敢肆讥侮。使当日苦心至衷。晦昧剥蚀而莫之惜焉。虽谓之无人心可也。夫空言无实。孔孟已不能免。然则孔孟亦可侮欤。孝庙之训曰。苟能声大义于天下。虽覆亡非所恤也。圣志卓然。诚非群下所及。而以人臣谋国之道言之。又安可不量时势。轻举妄动。置君父于必危之地哉。是以当时任事诸贤之造膝陈谟也。固尝曰自强图治。以俟几会。而又请密通南朝。以伸诚款。且探中原声息。是果何悖于义。而或者欲以景延广拟之。不亦舛乎。眉叟记言曰。两宋用事。劝上开辽左之役。上玉几铭。谏用兵事也。又何其谰谩无稽之甚也。若曰清人享国长久。式至今日。何几会之可俟云尔。则有大不然者。清人之享国至今。彼辈果能取必于百年之前耶。 孝庙临御十年。以己亥升遐。时则永历皇帝方在广东。诏令除拜。遍行于湖浙云贵之间。李定国桂林之役。清之亲王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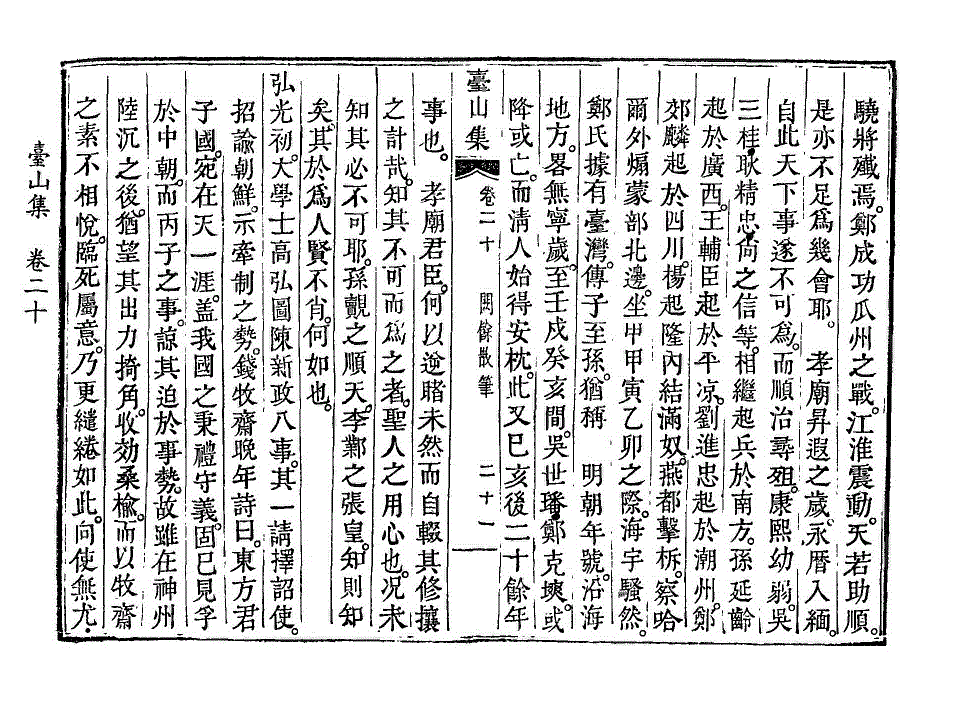 骁将歼焉。郑成功瓜州之战。江淮震动。天若助顺。是亦不足为几会耶。 孝庙升遐之岁。永历入缅。自此天下事遂不可为。而顺治寻殂。康熙幼弱。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起兵于南方。孙延龄起于广西。王辅臣起于平凉。刘进忠起于潮州。郑郊麟起于四川。杨起隆内结满奴。燕都击柝。察哈尔外煽蒙部北边。坐甲甲寅乙卯之际。海宇骚然。郑氏据有台湾。传子至孙。犹称 明朝年号。沿海地方。略无宁岁。至壬戌癸亥间。吴世璠,郑克塽。或降或亡。而清人始得安枕。此又己亥后二十馀年事也。 孝庙君臣。何以逆睹未然而自辍其修攘之计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圣人之用心也。况未知其必不可耶。孙觌之顺天。李邺之张皇。知则知矣。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骁将歼焉。郑成功瓜州之战。江淮震动。天若助顺。是亦不足为几会耶。 孝庙升遐之岁。永历入缅。自此天下事遂不可为。而顺治寻殂。康熙幼弱。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起兵于南方。孙延龄起于广西。王辅臣起于平凉。刘进忠起于潮州。郑郊麟起于四川。杨起隆内结满奴。燕都击柝。察哈尔外煽蒙部北边。坐甲甲寅乙卯之际。海宇骚然。郑氏据有台湾。传子至孙。犹称 明朝年号。沿海地方。略无宁岁。至壬戌癸亥间。吴世璠,郑克塽。或降或亡。而清人始得安枕。此又己亥后二十馀年事也。 孝庙君臣。何以逆睹未然而自辍其修攘之计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圣人之用心也。况未知其必不可耶。孙觌之顺天。李邺之张皇。知则知矣。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弘光初。大学士高弘图陈新政八事。其一请择诏使。招谕朝鲜。示牵制之势。钱牧斋晚年诗曰。东方君子国。宛在天一涯。盖我国之秉礼守义。固已见孚于中朝。而丙子之事。谅其迫于事势。故虽在神州陆沉之后。犹望其出力掎角。收效桑榆。而以牧斋之素不相悦。临死属意。乃更缱绻如此。向使无尤,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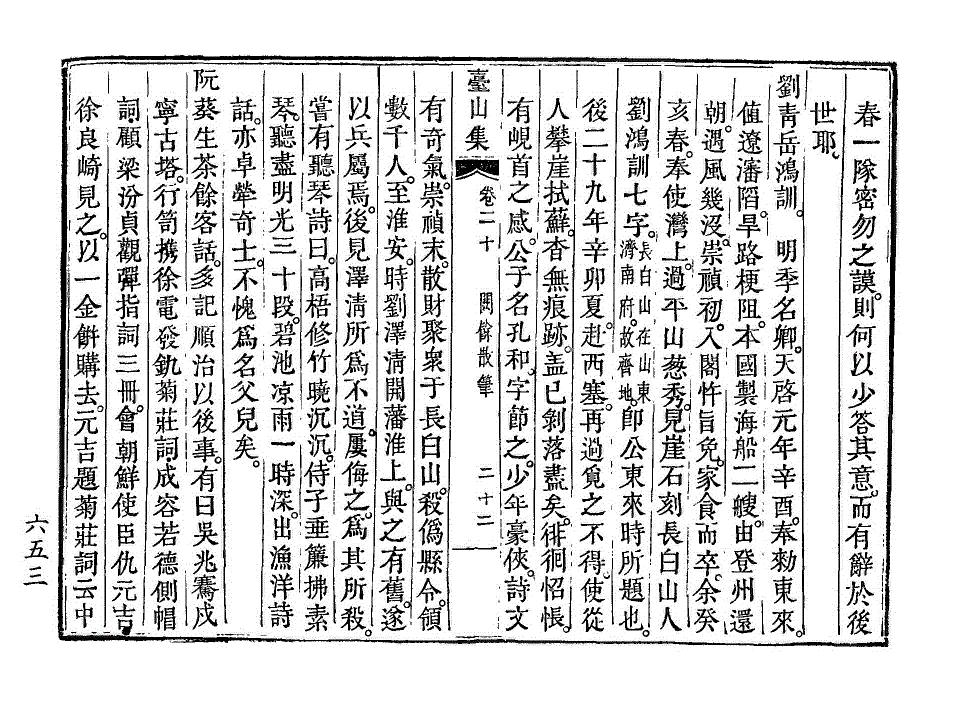 春一队密勿之谟。则何以少答其意。而有辞于后世耶。
春一队密勿之谟。则何以少答其意。而有辞于后世耶。刘青岳鸿训。 明季名卿。天启元年辛酉。奉敕东来。值辽沈陷。旱路梗阻。本国制海船二艘。由登州还朝。遇风几没。崇祯初。入阁忤旨免。家食而卒。余癸亥春。奉使湾上。过平山葱秀。见崖石刻长白山人刘鸿训七字。(长白山在山东济南府。故齐地。)即公东来时所题也。后二十九年辛卯夏。赴西塞。再过觅之不得。使从人攀崖拭藓。杳无痕迹。盖已剥落尽矣。徘徊怊怅。有岘首之感。公子名孔和。字节之。少年豪侠。诗文有奇气。崇祯末。散财聚众于长白山。杀伪县令。领数千人。至淮安。时刘泽清开藩淮上。与之有旧。遂以兵属焉。后见泽清所为不道。屡侮之。为其所杀。尝有听琴诗曰。高梧修竹晓沉沉。侍子垂帘拂素琴。听尽明光三十段。碧池凉雨一时深。出渔洋诗话。亦卓荦奇士。不愧为名父儿矣。
阮葵生茶馀客话。多记顺治以后事。有曰吴兆骞戍宁古塔。行笥携徐电发釚菊庄词,成容若德侧帽词,顾梁汾贞观弹指词三册。会朝鲜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见之。以一金饼购去。元吉题菊庄词云中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4H 页
 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良崎题侧帽弹指词云使车昨渡海东边。携得新词二妙传。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以高丽纸书之。寄来中国渔洋续集。咏此事云。考其时代。似在 本朝孝显间。而东使赴燕者。未闻有仇元吉,徐良崎。仇姓则绝无仕宦立朝者。尤属讹谬。岂使行书记伴倘中。有此二人。而遂以为朝鲜使臣欤。
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良崎题侧帽弹指词云使车昨渡海东边。携得新词二妙传。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以高丽纸书之。寄来中国渔洋续集。咏此事云。考其时代。似在 本朝孝显间。而东使赴燕者。未闻有仇元吉,徐良崎。仇姓则绝无仕宦立朝者。尤属讹谬。岂使行书记伴倘中。有此二人。而遂以为朝鲜使臣欤。显宗朝。 孝庙跻祔后。 仁宣大妃尊崇册礼。即当举行。而延拖过禫月。说者以为尊崇礼成。殿宫当受贺。而 王妃私期不远。当差退。以待其过。俞韨南棨在玉堂。上劄言其不可曰。 内殿私练之期。适当近旬。少迟册礼。兼伸私情。虽若无甚害理。而事无大小。渐不可不慎。此亦公私互胜。情礼相夺之端也。古名臣识虑之深远。言议之严正如此。
显庙二年。 上视学试士。尹尚书阶占第三。金相国锡胄占第四。大臣以肺腑嫌为言。盖金公于 明圣后为从兄也。 上命止取其魁。馀皆罢。金公世德之美。文章之高。非藉肺腑以取第者。当时所处。似涉过当。而盛际气象。可以想见。自后世论之。奚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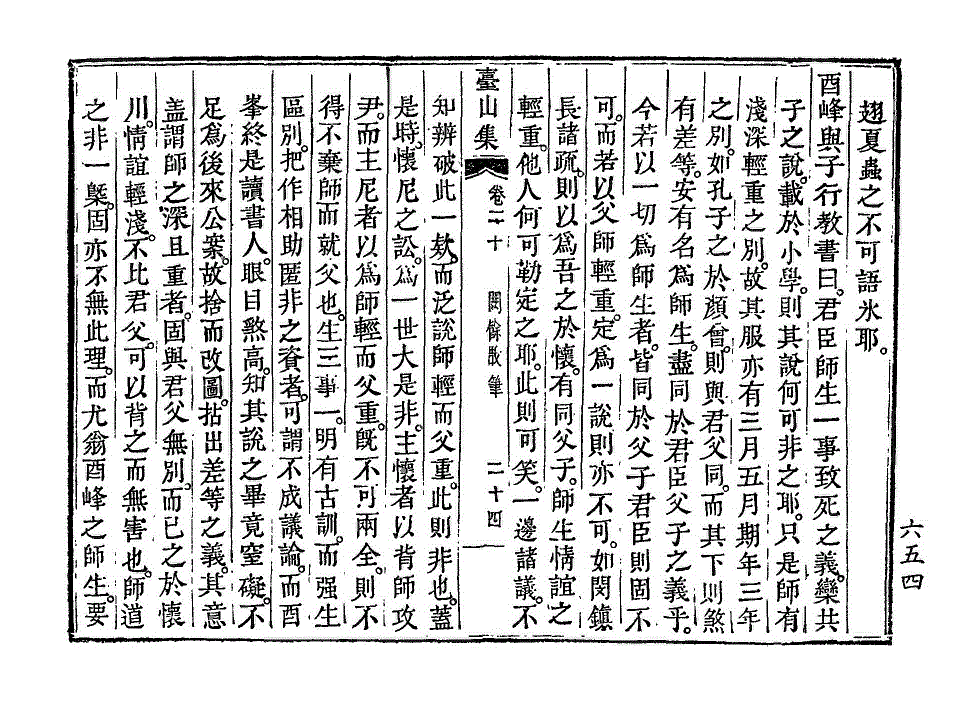 翅夏虫之不可语冰耶。
翅夏虫之不可语冰耶。酉峰与子行教书曰。君臣师生一事致死之义。栾共子之说。载于小学。则其说何可非之耶。只是师有浅深轻重之别。故其服亦有三月五月期年三年之别。如孔子之于颜曾。则与君父同。而其下则煞有差等。安有名为师生。尽同于君臣父子之义乎。今若以一切为师生者。皆同于父子君臣则固不可。而若以父师轻重。定为一说则亦不可。如闵镇长诸疏。则以为吾之于怀。有同父子。师生情谊之轻重。他人何可勒定之耶。此则可笑。一边诸议。不知辨破此一款。而泛说师轻而父重。此则非也。盖是时。怀尼之讼。为一世大是非。主怀者以背师攻尹。而主尼者以为师轻而父重。既不可两全。则不得不弃师而就父也。生三事一。明有古训。而强生区别。把作相助匿非之资者。可谓不成议论。而酉峰终是读书人。眼目煞高。知其说之毕竟窒碍。不足为后来公案。故舍而改图。拈出差等之义。其意盖谓师之深且重者。固与君父无别。而已之于怀川。情谊轻浅。不比君父。可以背之而无害也。师道之非一槩。固亦不无此理。而尤翁酉峰之师生。要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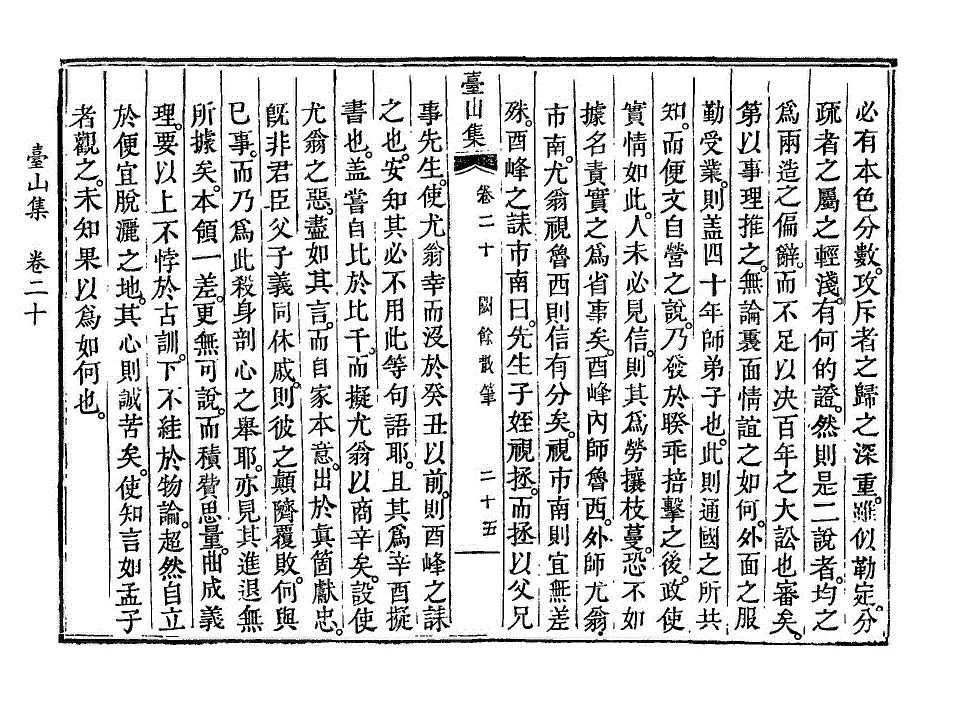 必有本色分数。攻斥者之归之深重。虽似勒定。分疏者之属之轻浅。有何的證。然则是二说者。均之为两造之偏辞。而不足以决百年之大讼也审矣。第以事理推之。无论里面情谊之如何。外面之服勤受业。则盖四十年师弟子也。此则通国之所共知。而便文自营之说。乃发于睽乖掊击之后。政使实情如此。人未必见信。则其为劳攘枝蔓。恐不如据名责实之为省事矣。酉峰内师鲁西。外师尤翁,韨南。尤翁视鲁西则信有分矣。视韨南则宜无差殊。酉峰之诔韨南曰。先生子侄视拯。而拯以父兄事先生。使尤翁幸而没于癸丑以前。则酉峰之诔之也。安知其必不用此等句语耶。且其为辛酉拟书也。盖尝自比于比干。而拟尤翁以商辛矣。设使尤翁之恶。尽如其言。而自家本意。出于真个献忠。既非君臣父子义同休戚。则彼之颠隮覆败。何与已事。而乃为此杀身剖心之举耶。亦见其进退无所据矣。本领一差。更无可说。而积费思量。曲成义理。要以上不悖于古训。下不絓于物论。超然自立于便宜脱洒之地。其心则诚苦矣。使知言如孟子者观之。未知果以为如何也。
必有本色分数。攻斥者之归之深重。虽似勒定。分疏者之属之轻浅。有何的證。然则是二说者。均之为两造之偏辞。而不足以决百年之大讼也审矣。第以事理推之。无论里面情谊之如何。外面之服勤受业。则盖四十年师弟子也。此则通国之所共知。而便文自营之说。乃发于睽乖掊击之后。政使实情如此。人未必见信。则其为劳攘枝蔓。恐不如据名责实之为省事矣。酉峰内师鲁西。外师尤翁,韨南。尤翁视鲁西则信有分矣。视韨南则宜无差殊。酉峰之诔韨南曰。先生子侄视拯。而拯以父兄事先生。使尤翁幸而没于癸丑以前。则酉峰之诔之也。安知其必不用此等句语耶。且其为辛酉拟书也。盖尝自比于比干。而拟尤翁以商辛矣。设使尤翁之恶。尽如其言。而自家本意。出于真个献忠。既非君臣父子义同休戚。则彼之颠隮覆败。何与已事。而乃为此杀身剖心之举耶。亦见其进退无所据矣。本领一差。更无可说。而积费思量。曲成义理。要以上不悖于古训。下不絓于物论。超然自立于便宜脱洒之地。其心则诚苦矣。使知言如孟子者观之。未知果以为如何也。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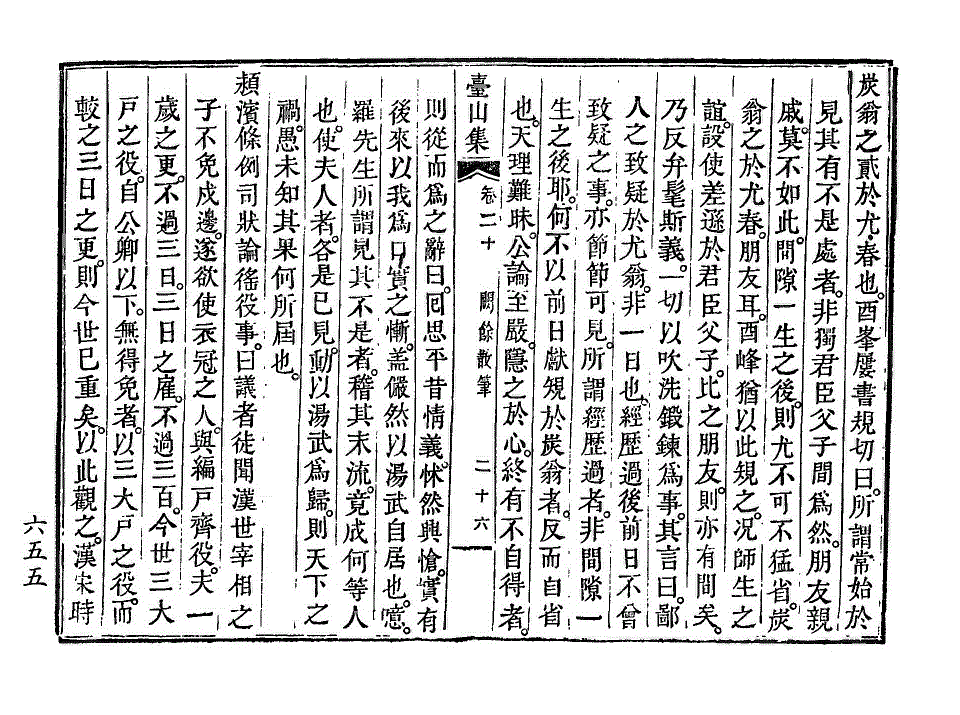 炭翁之贰于尤,春也。酉峰屡书规切曰。所谓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者。非独君臣父子间为然。朋友亲戚。莫不如此。间隙一生之后。则尤不可不猛省。炭翁之于尤春。朋友耳。酉峰犹以此规之。况师生之谊。设使差逊于君臣父子。比之朋友。则亦有间矣。乃反弁髦斯义。一切以吹洗锻鍊为事。其言曰。鄙人之致疑于尤翁。非一日也。经历过后前日不曾致疑之事。亦节节可见。所谓经历过者。非间隙一生之后耶。何不以前日献规于炭翁者。反而自省也。天理难昧。公论至严。隐之于心。终有不自得者。则从而为之辞曰。回思平昔情义。怵然兴怆。实有后来以我为口实之惭。盖俨然以汤武自居也。噫。罗先生所谓见其不是者。稽其末流。竟成何等人也。使夫人者。各是已见。动以汤武为归。则天下之祸。愚未知其果何所届也。
炭翁之贰于尤,春也。酉峰屡书规切曰。所谓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者。非独君臣父子间为然。朋友亲戚。莫不如此。间隙一生之后。则尤不可不猛省。炭翁之于尤春。朋友耳。酉峰犹以此规之。况师生之谊。设使差逊于君臣父子。比之朋友。则亦有间矣。乃反弁髦斯义。一切以吹洗锻鍊为事。其言曰。鄙人之致疑于尤翁。非一日也。经历过后前日不曾致疑之事。亦节节可见。所谓经历过者。非间隙一生之后耶。何不以前日献规于炭翁者。反而自省也。天理难昧。公论至严。隐之于心。终有不自得者。则从而为之辞曰。回思平昔情义。怵然兴怆。实有后来以我为口实之惭。盖俨然以汤武自居也。噫。罗先生所谓见其不是者。稽其末流。竟成何等人也。使夫人者。各是已见。动以汤武为归。则天下之祸。愚未知其果何所届也。颍滨条例司状论徭役事。曰议者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已重矣。以此观之。汉宋时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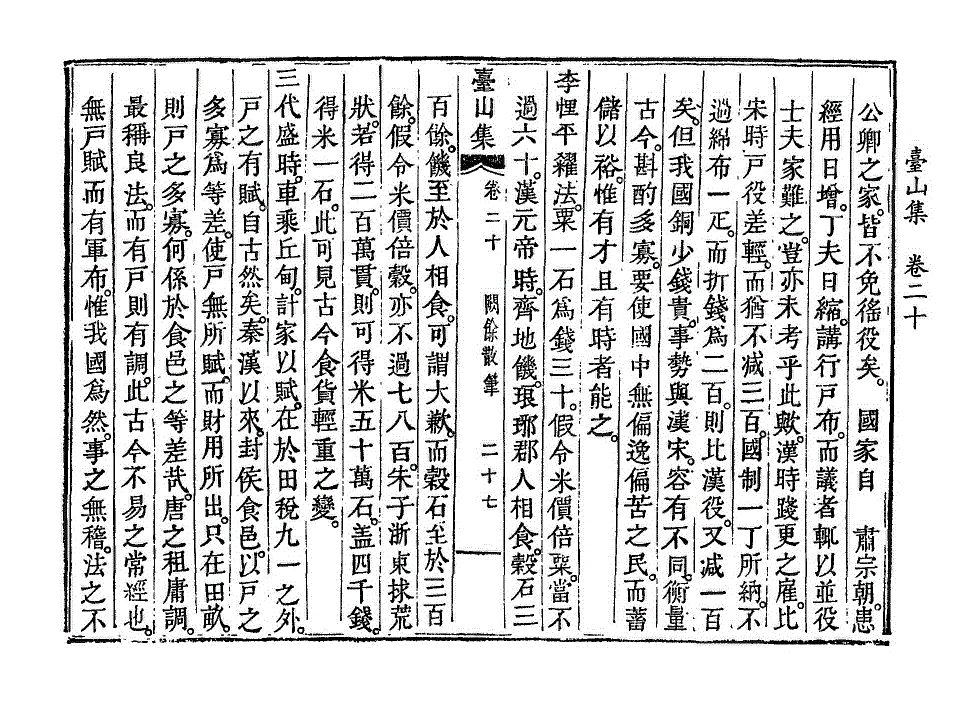 公卿之家。皆不免徭役矣。 国家自 肃宗朝。患经用日增。丁夫日缩。讲行户布。而议者辄以并役士夫家难之。岂亦未考乎此欤。汉时践更之雇。比宋时户役差轻。而犹不减三百。国制一丁所纳。不过绵布一疋。而折钱为二百。则比汉役。又减一百矣。但我国铜少钱贵。事势与汉宋。容有不同。衡量古今。斟酌多寡。要使国中无偏逸偏苦之民。而蓄储以裕。惟有才且有时者能之。
公卿之家。皆不免徭役矣。 国家自 肃宗朝。患经用日增。丁夫日缩。讲行户布。而议者辄以并役士夫家难之。岂亦未考乎此欤。汉时践更之雇。比宋时户役差轻。而犹不减三百。国制一丁所纳。不过绵布一疋。而折钱为二百。则比汉役。又减一百矣。但我国铜少钱贵。事势与汉宋。容有不同。衡量古今。斟酌多寡。要使国中无偏逸偏苦之民。而蓄储以裕。惟有才且有时者能之。李悝平籴法。粟一石为钱三十。假令米价倍粟。当不过六十。汉元帝时。齐地饥。琅琊郡人相食。谷石三百馀。饥至于人相食。可谓大歉。而谷石至于三百馀。假令米价倍谷。亦不过七八百。朱子浙东救荒状。若得二百万贯。则可得米五十万石。盖四千钱。得米一石。此可见古今食货轻重之变。
三代盛时。车乘丘甸。计家以赋。在于田税九一之外。户之有赋自古然矣。秦汉以来。封侯食邑。以户之多寡为等差。使户无所赋。而财用所出。只在田亩。则户之多寡。何系于食邑之等差哉。唐之租庸调。最称良法。而有户则有调。此古今不易之常经也。无户赋而有军布。惟我国为然。事之无稽。法之不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6L 页
 善。无甚于此。
善。无甚于此。兵民不分。古制非不美矣。后世多事。兵不可一日无。而击刺之技。操鍊之法。愈出愈新。亦不可夫人而能之也。于是简丁定额。分隶营卫。名之曰兵。专习战阵。以备不虞。课役征徭。一切蠲免。使为兵者。无事则不损毫发。稳享太平之乐。有事则无惜肝脑。独任效死之用。其馀齐民之不为兵者。不问品流之贵贱。但校赀产之高下。按籍计户。出物入官。时平则资国用。世乱则供军需。如唐元和间。天下税户一百四十四万。宿兵八十三万。大率以二户资一兵是已。此三代以后。兵民之所以分也。民出财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劳逸相当。彼此俱便。虽非古制。亦协时宜。圣王复作。亦不能易也。我国则不然。八路数千里。户不下数十万。而寸丝铢铜。不入县官。揆之事理。已甚无谓。而所谓军布者。内外营阃。签民为军。各有簿籍。专以徵布为事。而衣冠之族不与焉。所签者止是蠢蠢小民服勤田亩之类耳。役既偏苦。名又至贱。弱者不堪其苦。流亡四散。强者不堪其贱。避免百方。由是田畴日荒。丁夫日缩。黄口白骨。冤彻天壤。而窜窃谱籍。假冒氏姓。游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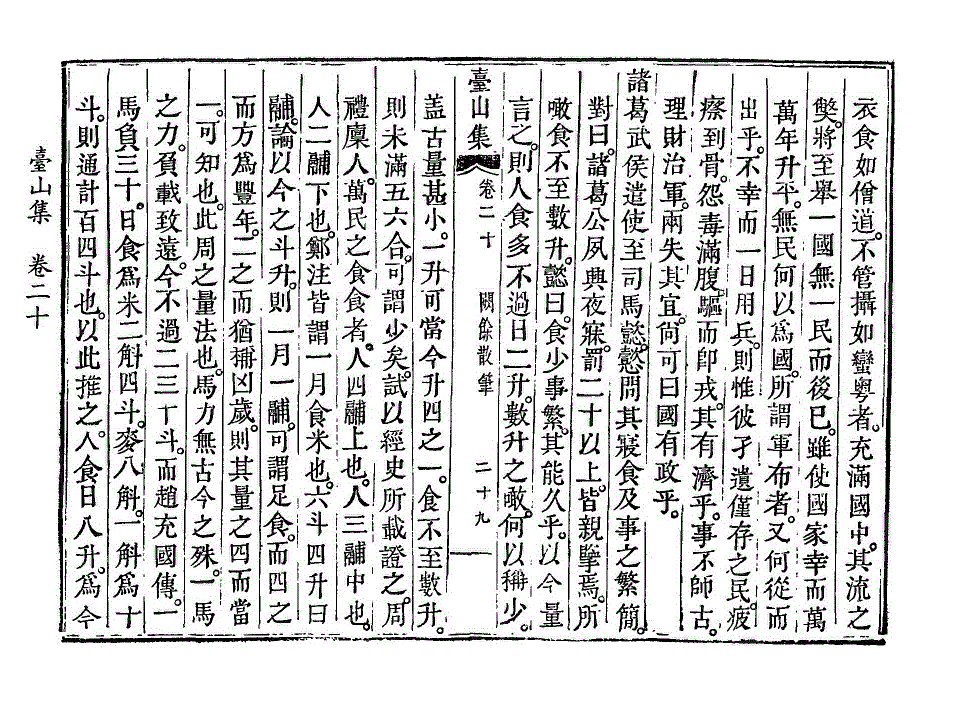 衣食如僧道。不管摄如蛮粤者。充满国中。其流之弊。将至举一国无一民而后已。虽使国家幸而万万年升平。无民何以为国。所谓军布者。又何从而出乎。不幸而一日用兵。则惟彼孑遗仅存之民。疲瘵到骨。怨毒满腹。驱而即戎。其有济乎。事不师古。理财治军。两失其宜。尚可曰国有政乎。
衣食如僧道。不管摄如蛮粤者。充满国中。其流之弊。将至举一国无一民而后已。虽使国家幸而万万年升平。无民何以为国。所谓军布者。又何从而出乎。不幸而一日用兵。则惟彼孑遗仅存之民。疲瘵到骨。怨毒满腹。驱而即戎。其有济乎。事不师古。理财治军。两失其宜。尚可曰国有政乎。诸葛武侯遣使至司马懿。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繁简。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懿曰。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以今量言之。则人食多不过日二升。数升之啖。何以称少。盖古量甚小。一升可当今升四之一。食不至数升。则未满五六合。可谓少矣。试以经史所载證之。周礼廪人。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郑注皆谓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釜。论以今之斗升。则一月一釜。可谓足食。而四之而方为丰年。二之而犹称凶岁。则其量之四而当一。可知也。此周之量法也。马力无古今之殊。一马之力。负载致远。今不过二三十斗。而赵充国传。一马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一斛为十斗。则通计百四斗也。以此推之。人食日八升。为今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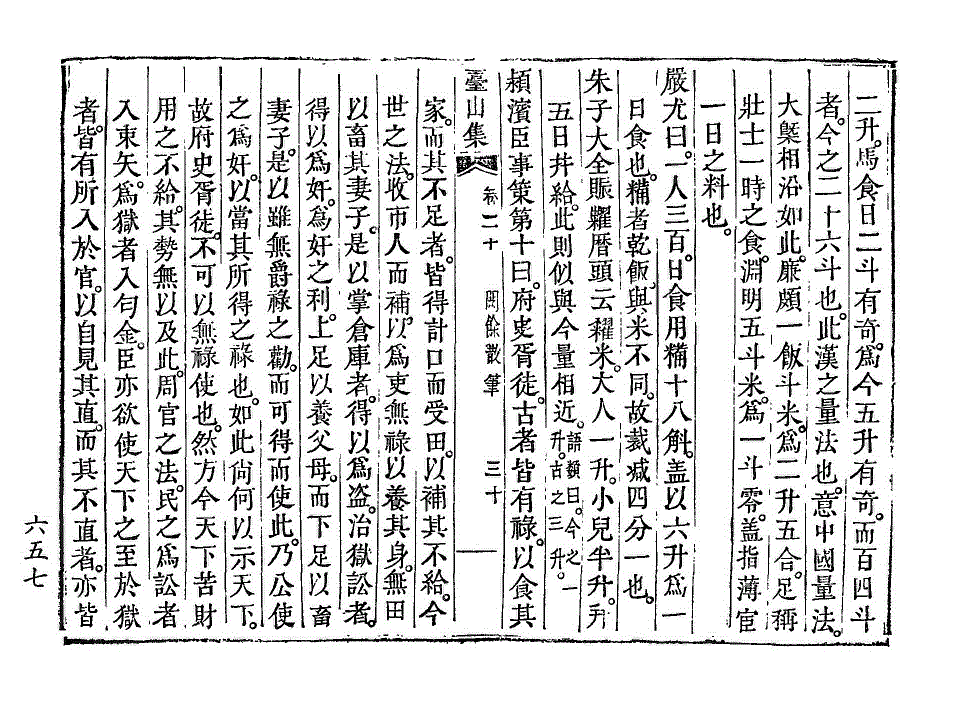 二升。马食日二斗有奇。为今五升有奇。而百四斗者。今之二十六斗也。此汉之量法也。意中国量法。大槩相沿如此。廉颇一饭斗米。为二升五合。足称壮士一时之食。渊明五斗米。为一斗零。盖指薄宦一日之料也。
二升。马食日二斗有奇。为今五升有奇。而百四斗者。今之二十六斗也。此汉之量法也。意中国量法。大槩相沿如此。廉颇一饭斗米。为二升五合。足称壮士一时之食。渊明五斗米。为一斗零。盖指薄宦一日之料也。严尤曰。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盖以六升为一日食也。糒者乾饭。与米不同。故裁减四分一也。
朱子大全赈粜历头云籴米。大人一升。小儿半升。并五日并给。此则似与今量相近。(语类曰。今之一升。古之三升。)
颍滨臣事策第十曰。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禄。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计口而受田。以补其不给。今世之法。收韨人而补。以为吏无禄以养其身。无田以畜其妻子。是以掌仓库者。得以为盗。治狱讼者。得以为奸。为奸之利。上足以养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是以虽无爵禄之劝。而可得而使此。乃公使之为奸。以当其所得之禄也。如此尚何以示天下。故府史胥徒。不可以无禄使也。然方今天下苦财用之不给。其势无以及此。周官之法。民之为讼者入束矢。为狱者入匀金。臣亦欲使天下之至于狱者。皆有所入于官。以自见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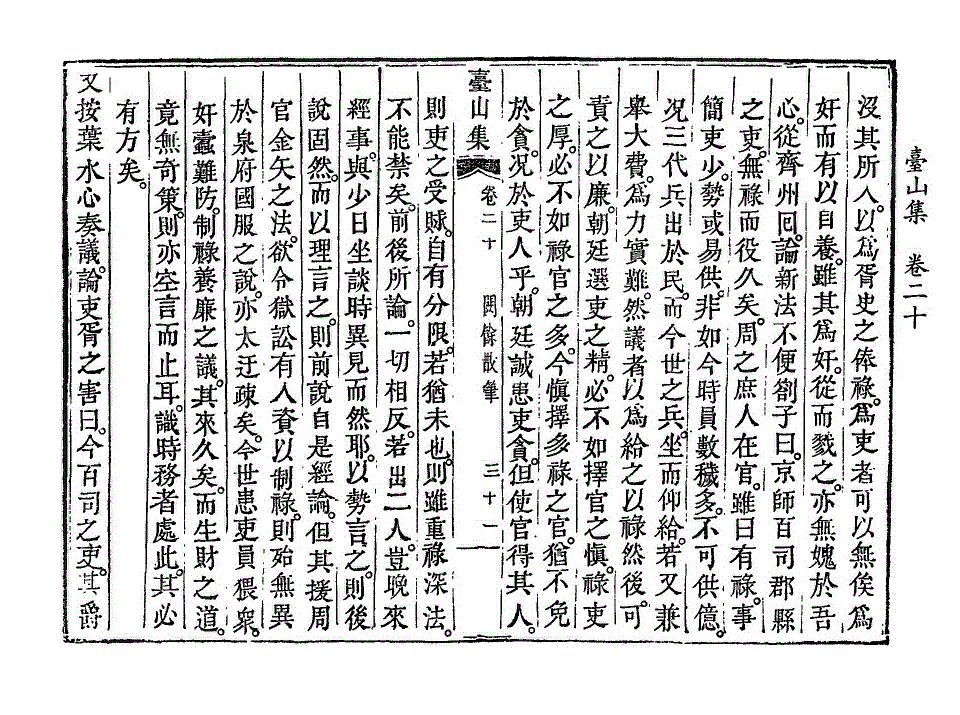 没其所人。以为胥史之俸禄。为吏者可以无俟为奸而有以自养。虽其为奸。从而戮之。亦无愧于吾心。从齐州回。论新法不便劄子曰。京师百司郡县之吏。无禄而役久矣。周之庶人在官。虽曰有禄。事简吏少。势或易供。非如今时员数秽多。不可供亿。况三代兵出于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给。若又兼举大费。为力实难。然议者以为给之以禄然后。可责之以廉。朝延选吏之精。必不如择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择多禄之官。犹不免于贪。况于吏人乎。朝廷诚患吏贪。但使官得其人。则吏之受赇。自有分限。若犹未也。则虽重禄深法。不能禁矣。前后所论。一切相反。若出二人。岂晚来经事。与少日坐谈时异见而然耶。以势言之。则后说固然。而以理言之。则前说自是经论。但其援周官金矢之法。欲令狱讼有人资以制禄。则殆无异于泉府国服之说。亦太迂疏矣。今世患吏员猥众。奸蠹难防。制禄养廉之议。其来久矣。而生财之道。竟无奇策。则亦空言而止耳。识时务者处此。其必有方矣。
没其所人。以为胥史之俸禄。为吏者可以无俟为奸而有以自养。虽其为奸。从而戮之。亦无愧于吾心。从齐州回。论新法不便劄子曰。京师百司郡县之吏。无禄而役久矣。周之庶人在官。虽曰有禄。事简吏少。势或易供。非如今时员数秽多。不可供亿。况三代兵出于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给。若又兼举大费。为力实难。然议者以为给之以禄然后。可责之以廉。朝延选吏之精。必不如择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择多禄之官。犹不免于贪。况于吏人乎。朝廷诚患吏贪。但使官得其人。则吏之受赇。自有分限。若犹未也。则虽重禄深法。不能禁矣。前后所论。一切相反。若出二人。岂晚来经事。与少日坐谈时异见而然耶。以势言之。则后说固然。而以理言之。则前说自是经论。但其援周官金矢之法。欲令狱讼有人资以制禄。则殆无异于泉府国服之说。亦太迂疏矣。今世患吏员猥众。奸蠹难防。制禄养廉之议。其来久矣。而生财之道。竟无奇策。则亦空言而止耳。识时务者处此。其必有方矣。又按叶水心奏议。论吏胥之害曰。今百司之吏。其爵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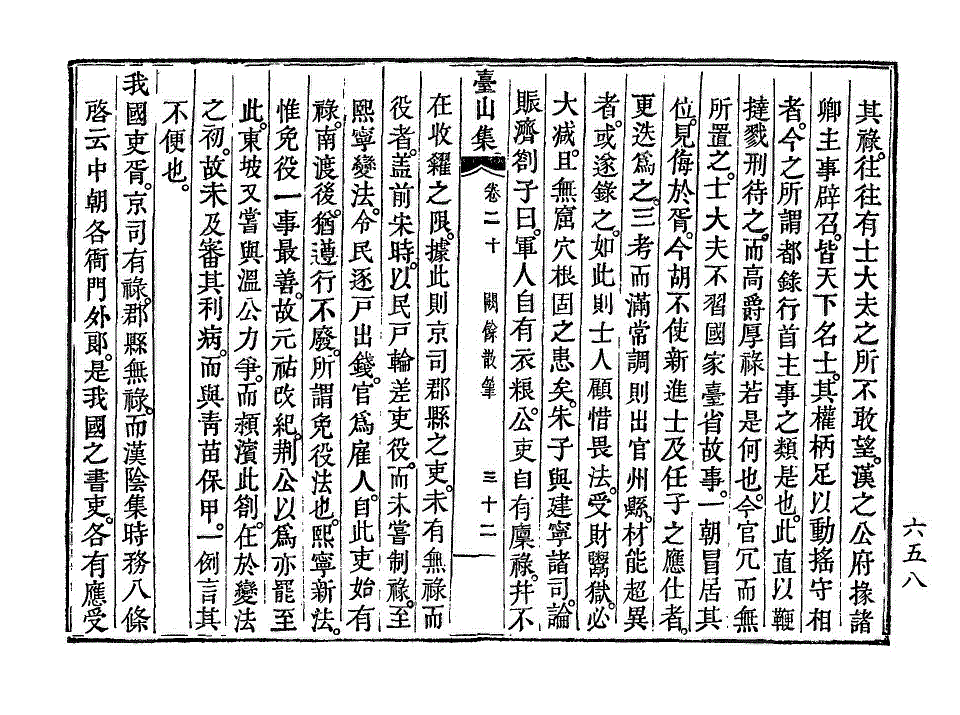 其禄。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汉之公府掾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此直以鞭挞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禄若是何也。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朝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官州县。材能超异者。或遂录之。如此则士人顾惜畏法。受财鬻狱。必大减。且无窟穴根固之患矣。朱子与建宁诸司。论赈济劄子曰。军人自有衣粮。公吏自有廪禄。并不在收籴之限。据此则京司郡县之吏。未有无禄而役者。盖前宋时。以民户轮差吏役。而未尝制禄。至熙宁变法。令民逐户出钱。官为雇人。自此吏始有禄。南渡后。犹遵行不废。所谓免役法也。熙宁新法。惟免役一事最善。故元祐改纪。荆公以为亦罢至此。东坡又尝与温公力争。而颍滨此劄。在于变法之初。故未及审其利病。而与青苗保甲。一例言其不便也。
其禄。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汉之公府掾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此直以鞭挞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禄若是何也。今官冗而无所置之。士大夫不习国家台省故事。一朝冒居其位。见侮于胥。今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官州县。材能超异者。或遂录之。如此则士人顾惜畏法。受财鬻狱。必大减。且无窟穴根固之患矣。朱子与建宁诸司。论赈济劄子曰。军人自有衣粮。公吏自有廪禄。并不在收籴之限。据此则京司郡县之吏。未有无禄而役者。盖前宋时。以民户轮差吏役。而未尝制禄。至熙宁变法。令民逐户出钱。官为雇人。自此吏始有禄。南渡后。犹遵行不废。所谓免役法也。熙宁新法。惟免役一事最善。故元祐改纪。荆公以为亦罢至此。东坡又尝与温公力争。而颍滨此劄。在于变法之初。故未及审其利病。而与青苗保甲。一例言其不便也。我国吏胥。京司有禄。郡县无禄。而汉阴集时务八条启云中朝各衙门外郎。是我国之书吏。各有应受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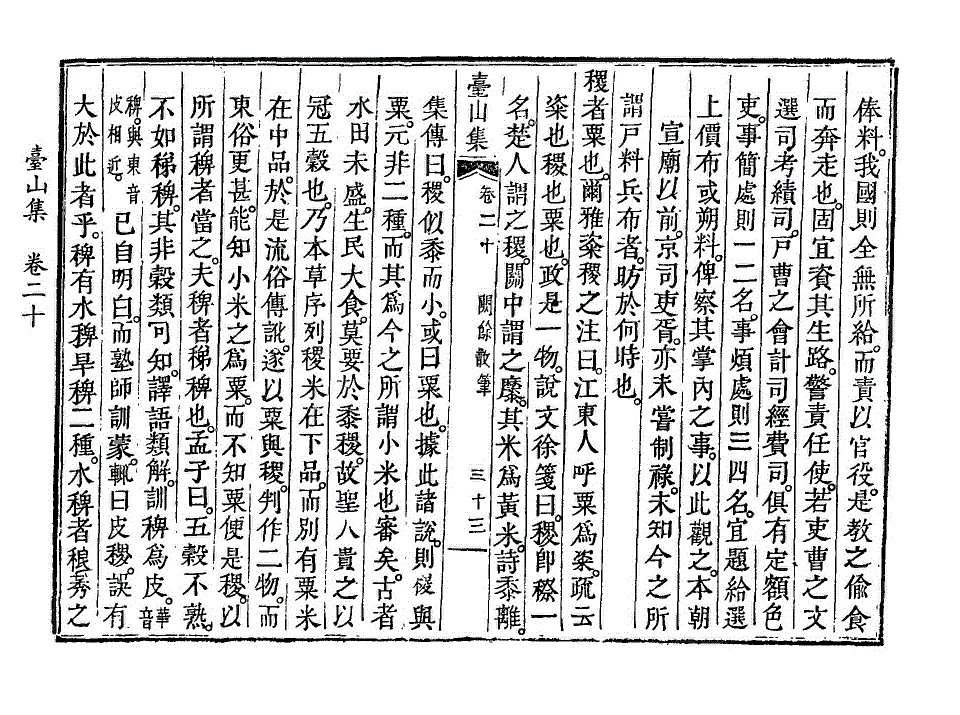 俸料。我国则全无所给。而责以官役。是教之偷食而奔走也。固宜资其生路。警责任使。若吏曹之文选司,考绩司。户曹之会计司,经费司。俱有定额色吏。事简处则一二名。事烦处则三四名。宜题给选上价布或朔料。俾察其掌内之事。以此观之。本朝 宣庙以前。京司吏胥。亦未尝制禄。未知今之所谓户料兵布者。昉于何时也。
俸料。我国则全无所给。而责以官役。是教之偷食而奔走也。固宜资其生路。警责任使。若吏曹之文选司,考绩司。户曹之会计司,经费司。俱有定额色吏。事简处则一二名。事烦处则三四名。宜题给选上价布或朔料。俾察其掌内之事。以此观之。本朝 宣庙以前。京司吏胥。亦未尝制禄。未知今之所谓户料兵布者。昉于何时也。稷者粟也。尔雅粢稷之注曰。江东人呼粟为粢。疏云粢也稷也粟也。政是一物。说文徐笺曰。稷即穄一名。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𪎭。其米为黄米。诗黍离。集传曰。稷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据此诸说。则稷与粟。元非二种。而其为今之所谓小米也审矣。古者水田未盛。生民大食。莫要于黍稷。故圣人贵之以冠五谷也。乃本草序列稷米在下品。而别有粟米在中品。于是流俗传讹。遂以粟与稷。判作二物。而东俗更甚。能知小米之为粟。而不知粟便是稷。以所谓稗者当之。夫稗者稊稗也。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稊稗。其非谷类可知。译语类解。训稗为皮。(华音稗。与东音皮相近。)已自明白。而塾师训蒙。辄曰皮稷。误有大于此者乎。稗有水稗旱稗二种。水稗者稂莠之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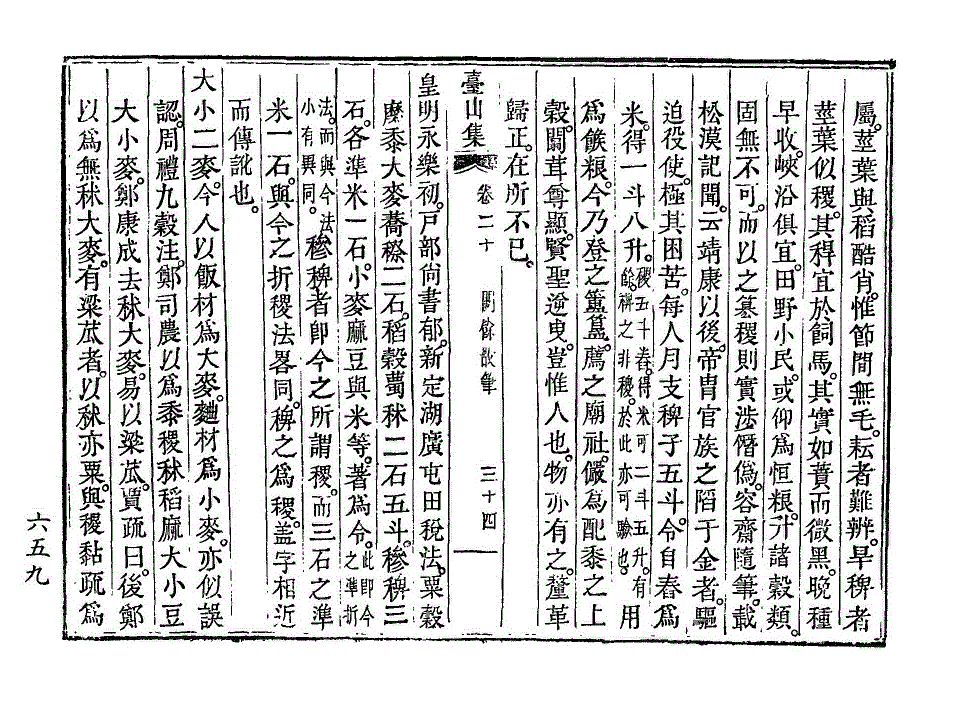 属。茎叶与稻酷肖。惟节间无毛。耘者难辨。旱稗者茎叶似稷。其秆宜于饲马。其实如蕡而微黑。晚种早收。峡沿俱宜。田野小民。或仰为恒粮。升诸谷类。固无不可。而以之篡稷则实涉僭伪。容斋随笔。载松漠记闻。云靖康以后。帝胄官族之陷于金者。驱迫役使。极其困苦。每人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稷五十舂。得米可二斗五升。有馀。稗之非稷。于此亦可验也。)用为糇粮。今乃登之簠簋。荐之庙社。俨为配黍之上谷。阘茸尊显。贤圣逆曳。岂惟人也。物亦有之。釐革归正。在所不已。
属。茎叶与稻酷肖。惟节间无毛。耘者难辨。旱稗者茎叶似稷。其秆宜于饲马。其实如蕡而微黑。晚种早收。峡沿俱宜。田野小民。或仰为恒粮。升诸谷类。固无不可。而以之篡稷则实涉僭伪。容斋随笔。载松漠记闻。云靖康以后。帝胄官族之陷于金者。驱迫役使。极其困苦。每人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稷五十舂。得米可二斗五升。有馀。稗之非稷。于此亦可验也。)用为糇粮。今乃登之簠簋。荐之庙社。俨为配黍之上谷。阘茸尊显。贤圣逆曳。岂惟人也。物亦有之。釐革归正。在所不已。皇明永乐初。户部尚书郁。新定湖广屯田税法。粟谷𪎭黍大麦荞穄二石。稻谷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各准米一石。小麦麻豆与米等。著为令。(此即今之准折法。而与今法小有异同。)穇稗者即今之所谓稷。而三石之准米一石。与今之折稷法略同。稗之为稷。盖字相近而传讹也。
大小二麦。今人以饭材为大麦。曲材为小麦。亦似误认。周礼九谷注。郑司农以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康成去秫大麦。易以粱菰。贾疏曰。后郑以为无秫大麦。有粱菰者。以秫亦粟。与稷黏疏为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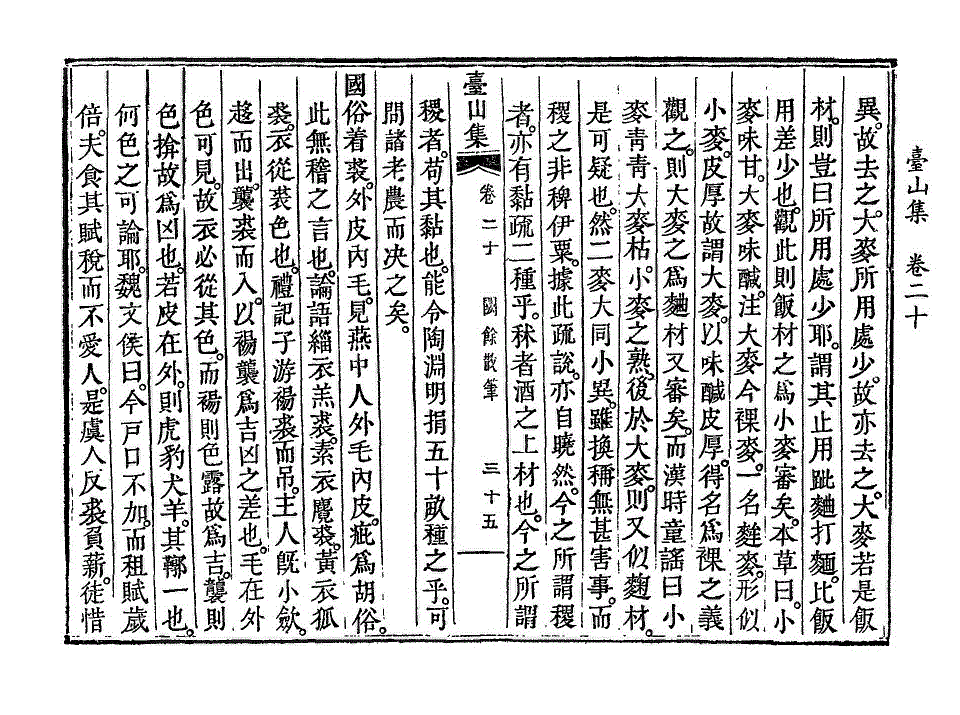 异。故去之。大麦所用处少。故亦去之。大麦若是饭材。则岂曰所用处少耶。谓其止用跐曲打面。比饭用差少也。观此则饭材之为小麦审矣。本草曰。小麦味甘。大麦味咸。注大麦今裸麦。一名麰麦。形似小麦。皮厚故谓大麦。以味咸皮厚。得名为裸之义观之。则大麦之为曲材又审矣。而汉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小麦之熟。后于大麦。则又似曲材。是可疑也。然二麦大同小异。虽换称无甚害事。而稷之非稗伊粟。据此疏说。亦自晓然。今之所谓稷者。亦有黏疏二种乎。秫者酒之上材也。今之所谓稷者。苟其黏也。能令陶渊明捐五十亩种之乎。可问诸老农而决之矣。
异。故去之。大麦所用处少。故亦去之。大麦若是饭材。则岂曰所用处少耶。谓其止用跐曲打面。比饭用差少也。观此则饭材之为小麦审矣。本草曰。小麦味甘。大麦味咸。注大麦今裸麦。一名麰麦。形似小麦。皮厚故谓大麦。以味咸皮厚。得名为裸之义观之。则大麦之为曲材又审矣。而汉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小麦之熟。后于大麦。则又似曲材。是可疑也。然二麦大同小异。虽换称无甚害事。而稷之非稗伊粟。据此疏说。亦自晓然。今之所谓稷者。亦有黏疏二种乎。秫者酒之上材也。今之所谓稷者。苟其黏也。能令陶渊明捐五十亩种之乎。可问诸老农而决之矣。国俗着裘。外皮内毛。见燕中人外毛内皮。疵为胡俗。此无稽之言也。论语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衣从裘色也。礼记子游裼裘而吊。主人既小敛。趍而出。袭裘而入。以裼袭为吉凶之差也。毛在外色可见。故衣必从其色。而裼则色露故为吉。袭则色掩故为凶也。若皮在外。则虎豹犬羊。其鞟一也。何色之可论耶。魏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夫食其赋税而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负薪。徒惜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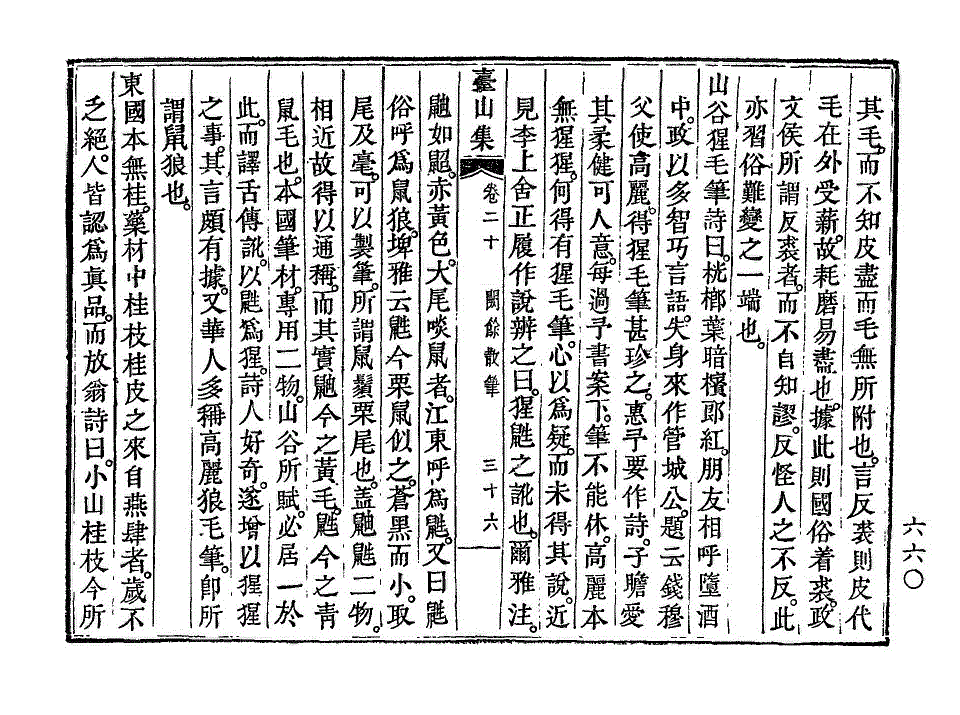 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也。言反裘则皮代毛在外受薪。故耗磨易尽也。据此则国俗着裘。政文侯所谓反裘者。而不自知谬。反怪人之不反。此亦习俗难变之一端也。
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也。言反裘则皮代毛在外受薪。故耗磨易尽也。据此则国俗着裘。政文侯所谓反裘者。而不自知谬。反怪人之不反。此亦习俗难变之一端也。山谷猩毛笔诗曰。桄榔叶暗槟郎红。朋友相呼堕酒中。政以多智巧言语。失身来作管城公。题云钱穆父使高丽。得猩毛笔甚珍之。惠予要作诗。子瞻爱其柔健可人意。每过予书案下。笔不能休。高丽本无猩猩。何得有猩毛笔。心以为疑。而未得其说。近见李上舍正履作说辨之曰。猩鼪之讹也。尔雅注。鼬如貂。赤黄色。大尾啖鼠者。江东呼为鼪。又曰鼪俗呼为鼠狼。埤雅云鼪今栗鼠似之。苍黑而小。取尾及毫。可以制笔。所谓鼠须栗尾也。盖鼬鼪二物。相近故得以通称。而其实鼬今之黄毛。鼪今之青鼠毛也。本国笔材。专用二物。山谷所赋。必居一于此。而译舌传讹。以鼪为猩。诗人好奇。遂增以猩猩之事。其言颇有据。又华人多称高丽狼毛笔。即所谓鼠狼也。
东国本无桂。药材中桂枝桂皮之来自燕肆者。岁不乏绝。人皆认为真品。而放翁诗曰。小山桂枝今所
台山集卷二十 第 6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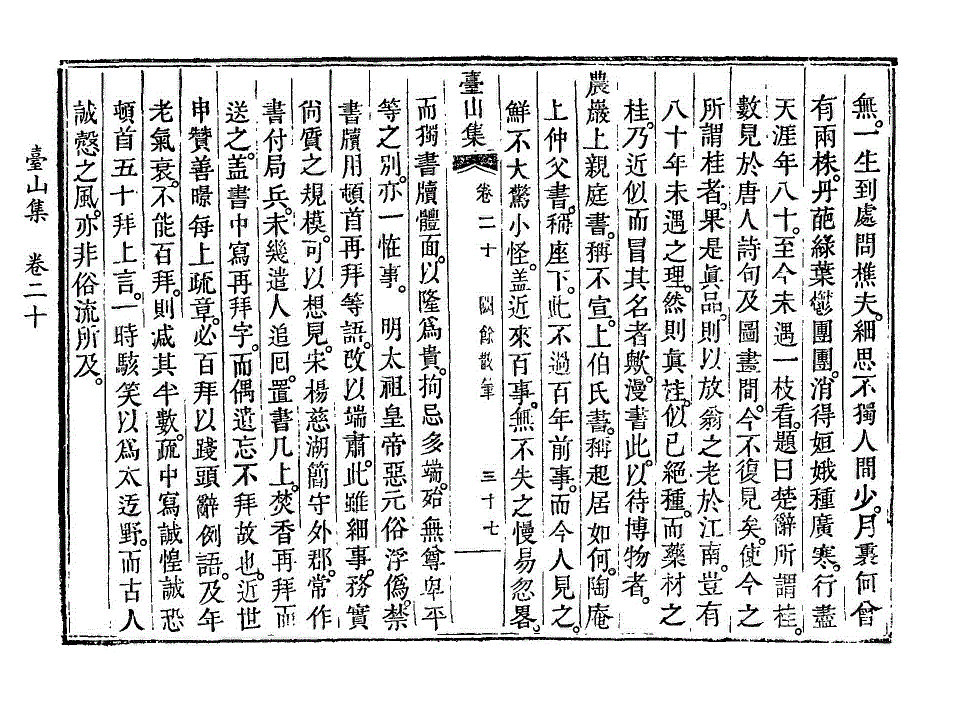 无。一生到处问樵夫。细思不独人间少。月里何曾有两株。丹葩绿叶郁团团。消得姮娥种广寒。行尽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题曰楚辞所谓桂。数见于唐人诗句及图画间。今不复见矣。使今之所谓桂者。果是真品。则以放翁之老于江南。岂有八十年未遇之理。然则真桂。似已绝种。而药材之桂。乃近似而冒其名者欤。漫书此。以待博物者。
无。一生到处问樵夫。细思不独人间少。月里何曾有两株。丹葩绿叶郁团团。消得姮娥种广寒。行尽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题曰楚辞所谓桂。数见于唐人诗句及图画间。今不复见矣。使今之所谓桂者。果是真品。则以放翁之老于江南。岂有八十年未遇之理。然则真桂。似已绝种。而药材之桂。乃近似而冒其名者欤。漫书此。以待博物者。农岩上亲庭书。称不宣。上伯氏书。称起居如何。陶庵上仲父书。称座下。此不过百年前事。而今人见之。鲜不大惊小怪。盖近来百事。无不失之慢易忽略。而独书牍体面。以隆为贵。拘忌多端。殆无尊卑平等之别。亦一怪事。 明太祖皇帝恶元俗浮伪。禁书牍用顿首再拜等语。改以端肃。此虽细事。务实尚质之规模。可以想见。宋杨慈湖简守外郡。常作书付局兵。未几遣人追回。置书几上。焚香再拜而送之。盖书中写再拜字。而偶遗忘不拜故也。近世申赞善暻每上疏章。必百拜以践头辞例语。及年老气衰。不能百拜。则减其半数。疏中写诚惶诚恐顿首五十拜上言。一时骇笑以为太迂野。而古人诚悫之风。亦非俗流所及。